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x 页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杂录]
[杂录]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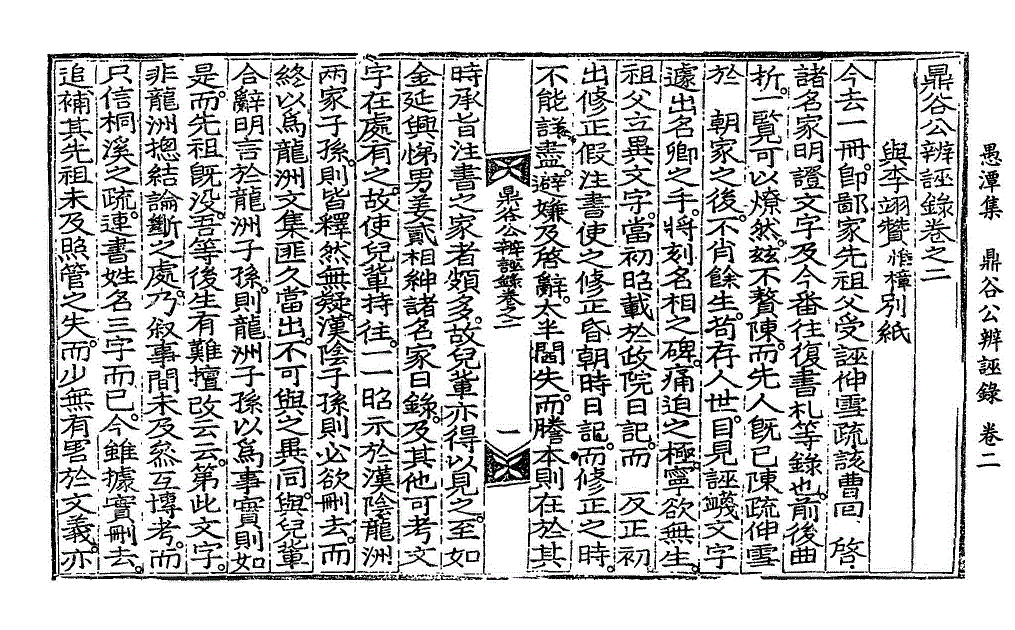 与李翊赞(惟樟)别纸
与李翊赞(惟樟)别纸今去一册。即鄙家先祖父受诬伸雪疏,该曹回 启,诸名家明證文字及今番往复书札等录也。前后曲折。一览可以燎然。玆不赘陈。而先人既已陈疏伸雪于 朝家之后。不肖馀生。苟存人世。目见诬蔑文字遽出名卿之手。将刻名相之碑。痛迫之极。宁欲无生。祖父立异文字。当初昭载于政院日记。而 反正初。出修正假注书使之修正昏朝时日记。而修正之时。不能详尽。避嫌及启辞。太半閪失。而誊本则在于其时承旨注书之家者颇多。故儿辈亦得以见之。至如金延兴悌男,姜贰相绅诸名家日录。及其他可考文字在处有之。故使儿辈持往。一一昭示于汉阴,龙洲两家子孙。则皆释然无疑。汉阴子孙则必欲删去。而终以为龙洲文集匪久当出。不可与之异同。与儿辈合辞明言于龙洲子孙。则龙洲子孙以为事实则如是。而先祖既没。吾等后生有难擅改云云。第此文字。非龙洲总结论断之处。乃叙事间未及参互博考。而只信桐溪之疏。连书姓名三字而已。今虽据实删去。追补其先祖未及照管之失。而少无有害于文义。亦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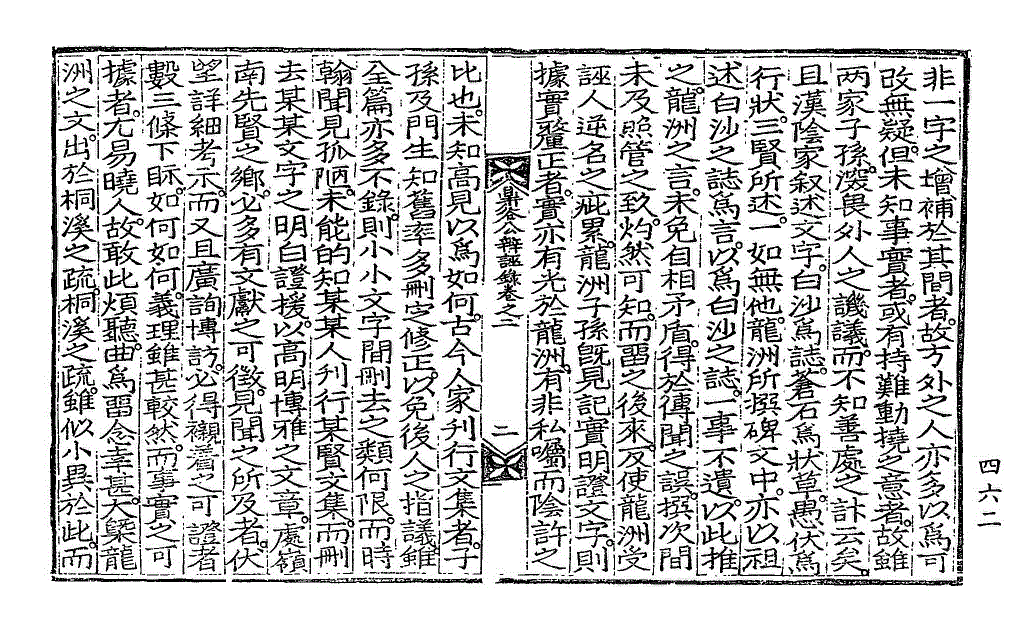 非一字之增补于其间者。故方外之人亦多以为可改无疑。但未知事实者。或有持难动挠之意者。故虽两家子孙。深畏外人之讥议。而不知善处之计云矣。且汉阴家叙述文字。白沙为志。苍石为状草。愚伏为行状。三贤所述。一如无他。龙洲所撰碑文中。亦以祖述白沙之志为言。以为白沙之志。一事不遗。以此推之。龙洲之言。未免自相矛盾。得于传闻之误。撰次间未及照管之致。灼然可知。而留之后来。反使龙洲受诬人逆名之疵累。龙洲子孙既见记实明證文字。则据实釐正者。实亦有光于龙洲。有非私嘱而阴许之比也。未知高见以为如何。古今人家刊行文集者。子孙及门生知旧率多删定修正。以免后人之指议。虽全篇亦多不录。则小小文字间删去之类何限。而时翰闻见孤陋。未能的知某某人刊行某贤文集。而删去某某文字之明白證援。以高明博雅之文章。处岭南先贤之乡。必多有文献之可徵。见闻之所及者。伏望详细考示。而又且广询博访。必得衬着之可證者数三条下视。如何如何。义理虽甚较然。而事实之可据者。尤易晓人。故敢此烦听。曲为留念幸甚。大槩龙洲之文。出于桐溪之疏。桐溪之疏。虽似小异于此。而
非一字之增补于其间者。故方外之人亦多以为可改无疑。但未知事实者。或有持难动挠之意者。故虽两家子孙。深畏外人之讥议。而不知善处之计云矣。且汉阴家叙述文字。白沙为志。苍石为状草。愚伏为行状。三贤所述。一如无他。龙洲所撰碑文中。亦以祖述白沙之志为言。以为白沙之志。一事不遗。以此推之。龙洲之言。未免自相矛盾。得于传闻之误。撰次间未及照管之致。灼然可知。而留之后来。反使龙洲受诬人逆名之疵累。龙洲子孙既见记实明證文字。则据实釐正者。实亦有光于龙洲。有非私嘱而阴许之比也。未知高见以为如何。古今人家刊行文集者。子孙及门生知旧率多删定修正。以免后人之指议。虽全篇亦多不录。则小小文字间删去之类何限。而时翰闻见孤陋。未能的知某某人刊行某贤文集。而删去某某文字之明白證援。以高明博雅之文章。处岭南先贤之乡。必多有文献之可徵。见闻之所及者。伏望详细考示。而又且广询博访。必得衬着之可證者数三条下视。如何如何。义理虽甚较然。而事实之可据者。尤易晓人。故敢此烦听。曲为留念幸甚。大槩龙洲之文。出于桐溪之疏。桐溪之疏。虽似小异于此。而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3H 页
 有桐溪之疏。故有龙洲之文。盖桐溪来自远外。传闻未详。忼慨之极。又遣辞不择。以至于此。而其时桐溪一队诸贤如愚伏郑公,苍石李公。皆与祖父交谊不少衰。故桐溪亦旋觉其误闻。其后乙亥年。桐溪与先人同为考官。人或劝先人不同入试院。先人以为此人只听传闻之讹误。而非出于私好恶。则吾不可以为私雠。至于避面。仍同入试场。罢试后。桐溪亟称于人曰。某人实是佳士。吾闻某人之父胜于其子。而吾之疏语为爽实云。悔无及矣。吾将于 筵中陈达云云。而(吴监司端氏来见先人言今日见桐溪。则其言如此云云。时翰亲听吴言。)匪久有丙子之乱。桐溪仍以下乡。此固鄙家之不幸也。此说既非文籍所记。有难见信。而其于明者之前。则不敢有隐。以此观之。桐溪则似已稔知其疏语之失实。而又闻龙洲之撰桐溪谥状。录其全疏。末谓某见公疏曰。吾未免千古罪人。遂日饮病死云。此固不肖之所未曾闻。虽未知其言之信否。而盖当初祖父出置之论。实出保全俱安之意。而出置之后。永昌奄至遘祸。国事渐至罔极。故祖父虽立异废论。出补岭海。而犹且慨念时事。深自悲愤。向人言语。辄发悔恨之辞。而桐溪疏中。亦有杀弟之论。则其在君子自反之道。引咎
有桐溪之疏。故有龙洲之文。盖桐溪来自远外。传闻未详。忼慨之极。又遣辞不择。以至于此。而其时桐溪一队诸贤如愚伏郑公,苍石李公。皆与祖父交谊不少衰。故桐溪亦旋觉其误闻。其后乙亥年。桐溪与先人同为考官。人或劝先人不同入试院。先人以为此人只听传闻之讹误。而非出于私好恶。则吾不可以为私雠。至于避面。仍同入试场。罢试后。桐溪亟称于人曰。某人实是佳士。吾闻某人之父胜于其子。而吾之疏语为爽实云。悔无及矣。吾将于 筵中陈达云云。而(吴监司端氏来见先人言今日见桐溪。则其言如此云云。时翰亲听吴言。)匪久有丙子之乱。桐溪仍以下乡。此固鄙家之不幸也。此说既非文籍所记。有难见信。而其于明者之前。则不敢有隐。以此观之。桐溪则似已稔知其疏语之失实。而又闻龙洲之撰桐溪谥状。录其全疏。末谓某见公疏曰。吾未免千古罪人。遂日饮病死云。此固不肖之所未曾闻。虽未知其言之信否。而盖当初祖父出置之论。实出保全俱安之意。而出置之后。永昌奄至遘祸。国事渐至罔极。故祖父虽立异废论。出补岭海。而犹且慨念时事。深自悲愤。向人言语。辄发悔恨之辞。而桐溪疏中。亦有杀弟之论。则其在君子自反之道。引咎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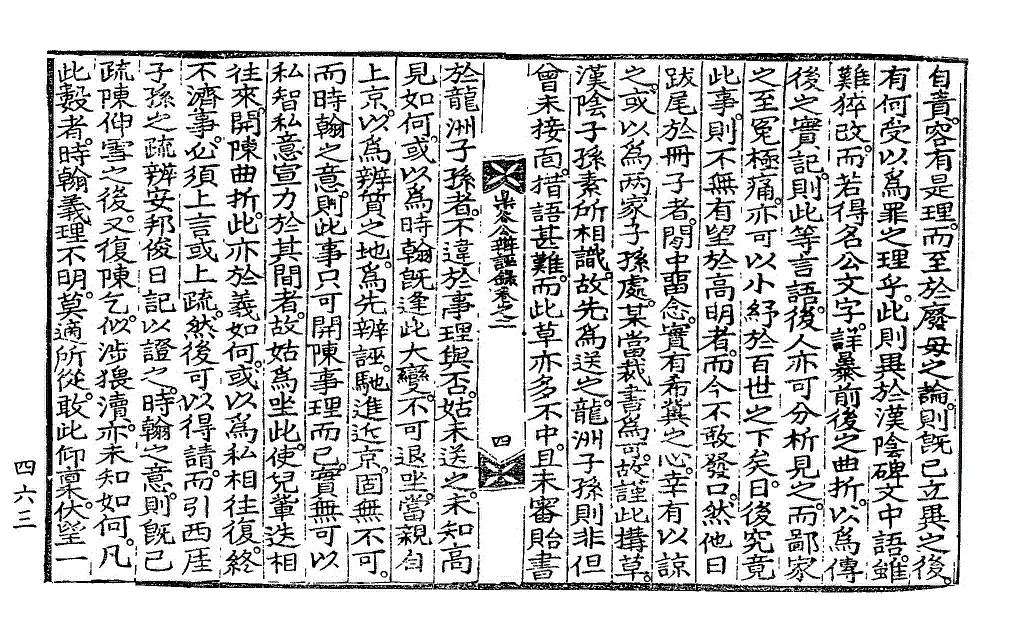 自责。容有是理。而至于废母之论。则既已立异之后。有何受以为罪之理乎。此则异于汉阴碑文中语。虽难猝改。而若得名公文字。详暴前后之曲折。以为传后之实记。则此等言语。后人亦可分析见之。而鄙家之至冤极痛。亦可以小纾于百世之下矣。日后究竟此事。则不无有望于高明者。而今不敢发口。然他日跋尾于册子者。閒中留念。实有希冀之心。幸有以谅之。或以为两家子孙处。某当裁书为可。故谨此搆草。汉阴子孙素所相识。故先为送之。龙洲子孙则非但曾未接面。措语甚难。而此草亦多不中。且未审贻书于龙洲子孙者。不违于事理与否。姑未送之。未知高见如何。或以为时翰既逢此大变。不可退坐。当亲自上京。以为辨质之地。为先辨诬。驰进近京。固无不可而时翰之意。则此事只可开陈事理而已。实无可以私智私意宣力于其间者。故姑为坐此。使儿辈迭相往来。开陈曲折。此亦于义如何。或以为私相往复。终不济事。必须上言或上疏。然后可以得请。而引西厓子孙之疏辨安邦俊日记以證之。时翰之意。则既已疏陈伸雪之后。又复陈乞。似涉猥渎。亦未知如何。凡此数者。时翰义理不明。莫适所从。敢此仰禀。伏望一
自责。容有是理。而至于废母之论。则既已立异之后。有何受以为罪之理乎。此则异于汉阴碑文中语。虽难猝改。而若得名公文字。详暴前后之曲折。以为传后之实记。则此等言语。后人亦可分析见之。而鄙家之至冤极痛。亦可以小纾于百世之下矣。日后究竟此事。则不无有望于高明者。而今不敢发口。然他日跋尾于册子者。閒中留念。实有希冀之心。幸有以谅之。或以为两家子孙处。某当裁书为可。故谨此搆草。汉阴子孙素所相识。故先为送之。龙洲子孙则非但曾未接面。措语甚难。而此草亦多不中。且未审贻书于龙洲子孙者。不违于事理与否。姑未送之。未知高见如何。或以为时翰既逢此大变。不可退坐。当亲自上京。以为辨质之地。为先辨诬。驰进近京。固无不可而时翰之意。则此事只可开陈事理而已。实无可以私智私意宣力于其间者。故姑为坐此。使儿辈迭相往来。开陈曲折。此亦于义如何。或以为私相往复。终不济事。必须上言或上疏。然后可以得请。而引西厓子孙之疏辨安邦俊日记以證之。时翰之意。则既已疏陈伸雪之后。又复陈乞。似涉猥渎。亦未知如何。凡此数者。时翰义理不明。莫适所从。敢此仰禀。伏望一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4H 页
 一指教。以解昏惑如何。时翰自逢此变以来。日夜痛迫。实无生意于人世。诚得高明特垂哀矜。指示可以处变之道。而明教义理之所当然。俾不至于昏惑失措。则时翰虽夕死。亦无憾矣。故委此陈禀。其间私书文字未及送。书札有非挂他人眼者。而悉以书送。盖欲高明之详悉事状。如一席面谈也。时翰之答洛下士友书别纸。儿辈亦恐反有所激。未能出示云。兄亦默会此意。勿以语人也。时翰之于高明。论交虽晚。情义无间平日所以仰恃而期望之者。实不后人。故私情所激。不避烦猥。有此缕缕。千万谅察。明白指教。毋孤日夕颙望之诚幸甚。
一指教。以解昏惑如何。时翰自逢此变以来。日夜痛迫。实无生意于人世。诚得高明特垂哀矜。指示可以处变之道。而明教义理之所当然。俾不至于昏惑失措。则时翰虽夕死。亦无憾矣。故委此陈禀。其间私书文字未及送。书札有非挂他人眼者。而悉以书送。盖欲高明之详悉事状。如一席面谈也。时翰之答洛下士友书别纸。儿辈亦恐反有所激。未能出示云。兄亦默会此意。勿以语人也。时翰之于高明。论交虽晚。情义无间平日所以仰恃而期望之者。实不后人。故私情所激。不避烦猥。有此缕缕。千万谅察。明白指教。毋孤日夕颙望之诚幸甚。李翊赞(惟樟)别纸
惟樟以僻乡孤陋。其于近代名贤事迹。全未有知。前冬偶叩仙扉留连之次。获睹先大夫昏朝时处变之迹。嘿叹世变之无穷。而先城主至诚格天之实。亦可谓万世之师范也。孰谓不幸之说。又出于名卿之笔。伏想左右情事。不知所以为喻。盖以两大贤子孙言之。其改之之得与不改之失。相距悬绝。何者。天下无两是者。名卿之言虽甚可信。而岂若当日奏 御文字。出于自己者之为可真实也。今之以删改为难云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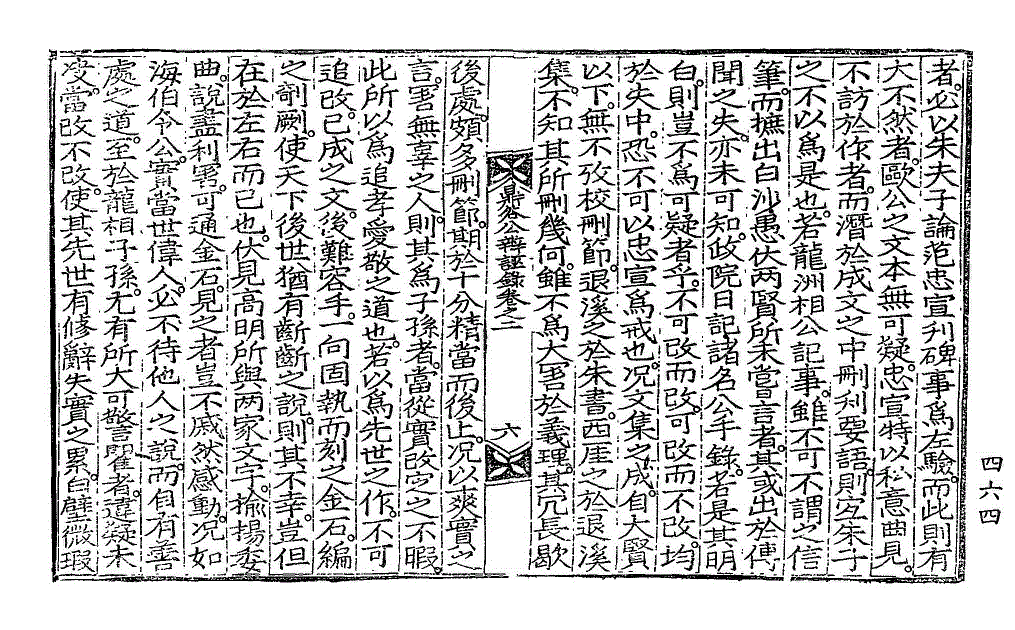 者。必以朱夫子论范忠宣刊碑事为左验。而此则有大不然者。欧公之文本无可疑。忠宣特以私意曲见。不访于作者。而潜于成文之中删刊要语。则宜朱子之不以为是也。若龙洲相公记事。虽不可不谓之信笔。而摭出白沙,愚伏两贤所未尝言者。其或出于传闻之失。亦未可知。政院日记,诸名公手录。若是其明白。则岂不为可疑者乎。不可改而改。可改而不改。均于失中。恐不可以忠宣为戒也。况文集之成。自大贤以下。无不考校删节。退溪之于朱书。西厓之于退溪集。不知其所删几何。虽不为大害于义理。其冗长歇后处。颇多删节。期于十分精当而后止。况以爽实之言。害无辜之人。则其为子孙者。当从实改定之不暇。此所以为追孝爱敬之道也。若以为先世之作。不可追改。已成之文。后难容手。一向固执而刻之金石。编之剞劂。使天下后世犹有龂龂之说。则其不幸。岂但在于左右而已也。伏见高明所与两家文字。揄扬委曲。说尽利害。可通金石。见之者岂不戚然感动。况如海伯令公。实当世伟人。必不待他人之说。而自有善处之道。至于龙相子孙。尤有所大可警瞿者。违疑未决。当改不改。使其先世有修辞失实之累。白璧微瑕
者。必以朱夫子论范忠宣刊碑事为左验。而此则有大不然者。欧公之文本无可疑。忠宣特以私意曲见。不访于作者。而潜于成文之中删刊要语。则宜朱子之不以为是也。若龙洲相公记事。虽不可不谓之信笔。而摭出白沙,愚伏两贤所未尝言者。其或出于传闻之失。亦未可知。政院日记,诸名公手录。若是其明白。则岂不为可疑者乎。不可改而改。可改而不改。均于失中。恐不可以忠宣为戒也。况文集之成。自大贤以下。无不考校删节。退溪之于朱书。西厓之于退溪集。不知其所删几何。虽不为大害于义理。其冗长歇后处。颇多删节。期于十分精当而后止。况以爽实之言。害无辜之人。则其为子孙者。当从实改定之不暇。此所以为追孝爱敬之道也。若以为先世之作。不可追改。已成之文。后难容手。一向固执而刻之金石。编之剞劂。使天下后世犹有龂龂之说。则其不幸。岂但在于左右而已也。伏见高明所与两家文字。揄扬委曲。说尽利害。可通金石。见之者岂不戚然感动。况如海伯令公。实当世伟人。必不待他人之说。而自有善处之道。至于龙相子孙。尤有所大可警瞿者。违疑未决。当改不改。使其先世有修辞失实之累。白璧微瑕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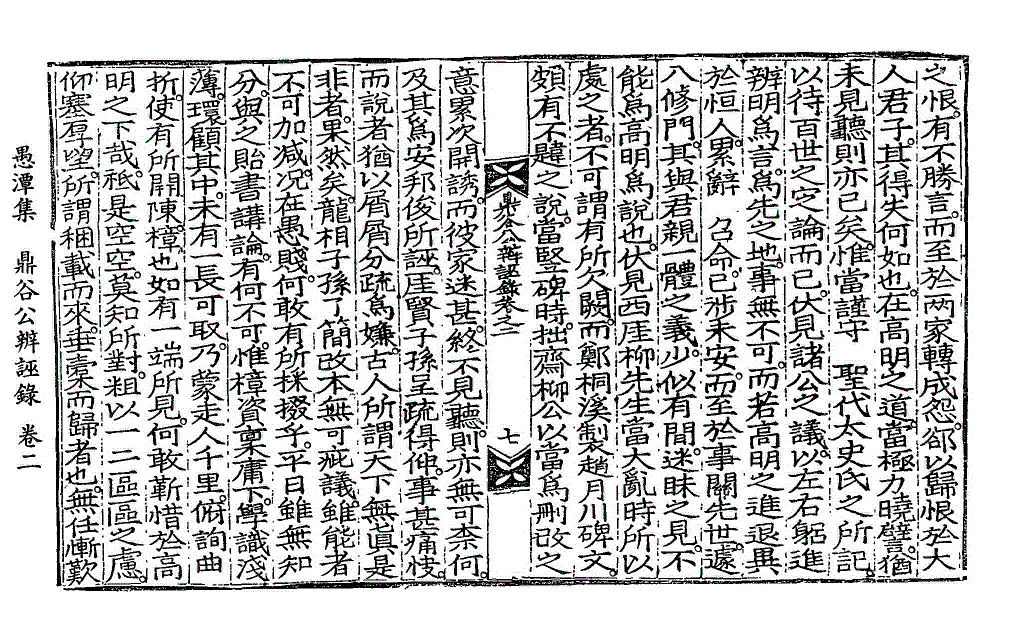 之恨。有不胜言。而至于两家转成怨。却以归恨于大人君子。其得失何如也。在高明之道。当极力晓譬。犹未见听则亦已矣。惟当谨守 圣代太史氏之所记。以待百世之定论而已。伏见诸公之议。以左右躬进辨明为言。为先之地。事无不可。而若高明之进退异于恒人。累辞 召命。已涉未安。而至于事关先世。遽入修门。其与君亲一体之义。少似有间。迷眛之见。不能为高明为说也。伏见西厓柳先生当大乱时所以处之者。不可谓有所欠阙。而郑桐溪制赵月川碑文。颇有不韪之说。当竖碑时。拙斋柳公以当为删改之意累次开诱。而彼家迷甚。终不见听。则亦无可柰何。及其为安邦俊所诬。厓贤子孙呈疏得伸。事甚痛快。而说者犹以屑屑分疏为嫌。古人所谓天下无真是非者。果然矣。龙相子孙了简改本无可疵议。虽能者不可加减。况在愚贱。何敢有所采掇乎。平日虽无知分。与之贻书讲论。有何不可。惟樟资禀庸下。学识浅薄。环顾其中。未有一长可取。乃蒙走人千里。俯询曲折。使有所开陈。樟也如有一端所见。何敢靳惜于高明之下哉。祗是空空。莫知所对。粗以一二区区之虑。仰塞厚望。所谓稛载而来。垂橐而归者也。无任惭叹
之恨。有不胜言。而至于两家转成怨。却以归恨于大人君子。其得失何如也。在高明之道。当极力晓譬。犹未见听则亦已矣。惟当谨守 圣代太史氏之所记。以待百世之定论而已。伏见诸公之议。以左右躬进辨明为言。为先之地。事无不可。而若高明之进退异于恒人。累辞 召命。已涉未安。而至于事关先世。遽入修门。其与君亲一体之义。少似有间。迷眛之见。不能为高明为说也。伏见西厓柳先生当大乱时所以处之者。不可谓有所欠阙。而郑桐溪制赵月川碑文。颇有不韪之说。当竖碑时。拙斋柳公以当为删改之意累次开诱。而彼家迷甚。终不见听。则亦无可柰何。及其为安邦俊所诬。厓贤子孙呈疏得伸。事甚痛快。而说者犹以屑屑分疏为嫌。古人所谓天下无真是非者。果然矣。龙相子孙了简改本无可疵议。虽能者不可加减。况在愚贱。何敢有所采掇乎。平日虽无知分。与之贻书讲论。有何不可。惟樟资禀庸下。学识浅薄。环顾其中。未有一长可取。乃蒙走人千里。俯询曲折。使有所开陈。樟也如有一端所见。何敢靳惜于高明之下哉。祗是空空。莫知所对。粗以一二区区之虑。仰塞厚望。所谓稛载而来。垂橐而归者也。无任惭叹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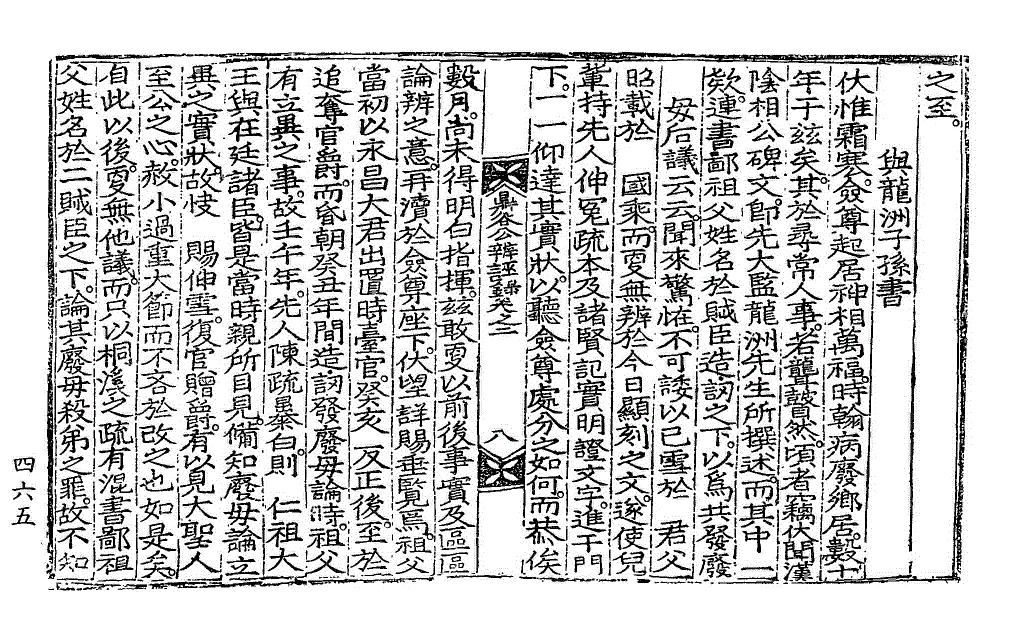 之至。
之至。与龙洲子孙书
伏惟霜寒。佥尊起居神相万福。时翰病废乡居。数十年于玆矣。其于寻常人事。若聋瞽然。顷者窃伏闻汉阴相公碑文。即先大监龙洲先生所撰述。而其中一款。连书鄙祖父姓名于贼臣造,讱之下。以为共发废 母后议云云。闻来惊怪。不可诿以已雪于 君父昭载于 国乘。而更无辨于今日显刻之文。遂使儿辈持先人伸冤疏本及诸贤记实明證文字。进干门下。一一仰达其实状。以听佥尊处分之如何。而恭俟数月。尚未得明白指挥。玆敢更以前后事实及区区论辨之意。再渎于佥尊座下。伏望详赐垂览焉。祖父当初以永昌大君出置时台官。癸亥 反正后。至于追夺官爵。而昏朝癸丑年间造,讱发废母论时。祖父有立异之事。故壬午年。先人陈疏暴白。则 仁祖大王与在廷诸臣。皆是当时亲所目见。备知废母论立异之实状。故快 赐伸雪。复官赠爵。有以见大圣人至公之心。赦小过重大节而不吝于改之也如是矣。自此以后。更无他议。而只以桐溪之疏有混书鄙祖父姓名于二贼臣之下。论其废母杀弟之罪。故不知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6H 页
 其前后事实者。骤见其混书。而或有致疑于其间者。今请陈之。呜呼。癸丑年间事。尚忍言哉。奸凶窃柄。煽俑飞语。上诬 慈殿。以为内作巫蛊。外应逆谋。将欲拥立永昌于宫中。宫府内外传说多端。其时名流之议。亦有出置永昌于阙外。远嫌避猜。则庶有俱安之望。故先祖出置之论。意实在此。而后来永昌奄至遘祸。此先祖之所以终身痛恨者也。及至废母之论。始发于造,讱。而合司席上。先祖即与崔公有源,金公止男,李公志完同辞斥之。其时立异。正当凶焰方起之初。故当时诸人。无不备知。 国乘野史。昭然俱载。佥尊亦已详览而备悉之矣。先祖遂见忤于时。出补岭海。当初心迹。一时名流举皆知之。而惟郑桐溪来自远外。初未知立异大论之事。只闻风传之误。以出置之启。为杀弟之权舆。故连书于造,讱之下。以为共发废母杀弟之论。其所为言殊不分明。有足以致人疑讶。而若使参考实状者观之。则犹可于混书之中。审其指意之各有所归。今此碑文则截去下段。与二贼臣连书。至称共发废母论。直断之以大逆不道之罪。天下宁有是事乎。夫废 君母。天下之大逆也。以大逆之名加之于人。天下之重事。苟非质诸人事之实
其前后事实者。骤见其混书。而或有致疑于其间者。今请陈之。呜呼。癸丑年间事。尚忍言哉。奸凶窃柄。煽俑飞语。上诬 慈殿。以为内作巫蛊。外应逆谋。将欲拥立永昌于宫中。宫府内外传说多端。其时名流之议。亦有出置永昌于阙外。远嫌避猜。则庶有俱安之望。故先祖出置之论。意实在此。而后来永昌奄至遘祸。此先祖之所以终身痛恨者也。及至废母之论。始发于造,讱。而合司席上。先祖即与崔公有源,金公止男,李公志完同辞斥之。其时立异。正当凶焰方起之初。故当时诸人。无不备知。 国乘野史。昭然俱载。佥尊亦已详览而备悉之矣。先祖遂见忤于时。出补岭海。当初心迹。一时名流举皆知之。而惟郑桐溪来自远外。初未知立异大论之事。只闻风传之误。以出置之启。为杀弟之权舆。故连书于造,讱之下。以为共发废母杀弟之论。其所为言殊不分明。有足以致人疑讶。而若使参考实状者观之。则犹可于混书之中。审其指意之各有所归。今此碑文则截去下段。与二贼臣连书。至称共发废母论。直断之以大逆不道之罪。天下宁有是事乎。夫废 君母。天下之大逆也。以大逆之名加之于人。天下之重事。苟非质诸人事之实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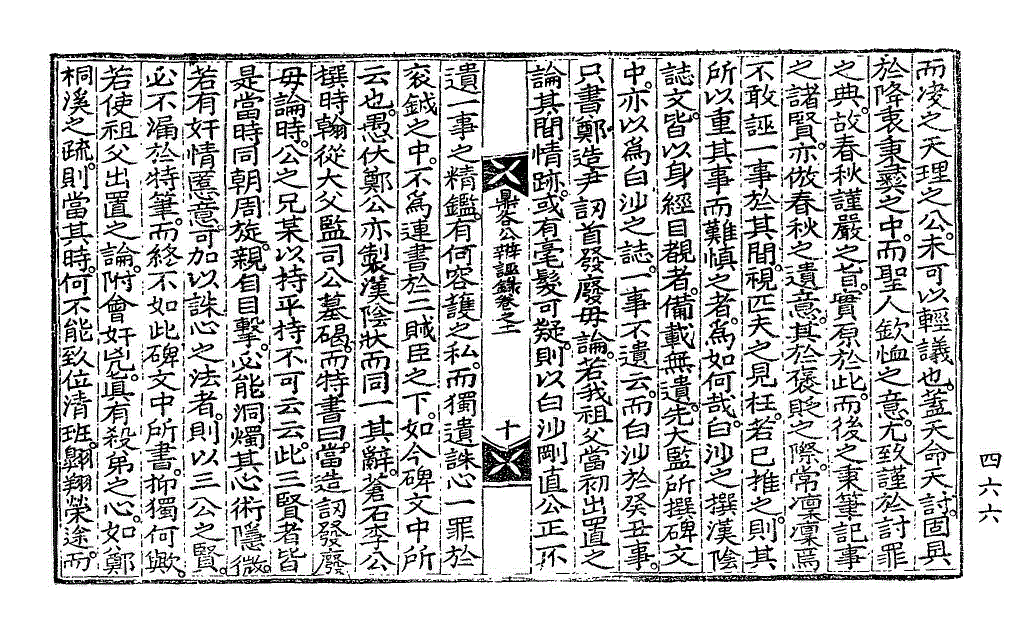 而决之天理之公。未可以轻议也。盖天命天讨。固具于降衷秉彝之中。而圣人钦恤之意。尤致谨于讨罪之典。故春秋谨严之旨。实原于此。而后之秉笔记事之诸贤。亦仿春秋之遗意。其于褒贬之际。常凛凛焉不敢诬一事于其间。视匹夫之见枉。若已推之。则其所以重其事而难慎之者。为如何哉。白沙之撰汉阴志文。皆以身经目睹者。备载无遗。先大监所撰碑文中。亦以为白沙之志。一事不遗云。而白沙于癸丑事。只书郑造,尹讱首发废母论。若我祖父当初出置之论其间情迹。或有毫发可疑。则以白沙刚直公正不遗一事之精鉴。有何容护之私。而独遗诛心一罪于衮钺之中。不为连书于二贼臣之下。如今碑文中所云也。愚伏郑公亦制汉阴状而同一其辞。苍石李公撰时翰从大父监司公墓碣。而特书曰。当造,讱发废母论时。公之兄某以持平持不可云云。此三贤者皆是当时同朝周旋。亲自目击。必能洞烛其心术隐微。若有奸情慝意。可加以诛心之法者。则以三公之贤。必不漏于特笔。而终不如此碑文中所书。抑独何欤。若使祖父出置之论。附会奸凶。真有杀弟之心。如郑桐溪之疏。则当其时。何不能致位清班。翱翔荣途。而
而决之天理之公。未可以轻议也。盖天命天讨。固具于降衷秉彝之中。而圣人钦恤之意。尤致谨于讨罪之典。故春秋谨严之旨。实原于此。而后之秉笔记事之诸贤。亦仿春秋之遗意。其于褒贬之际。常凛凛焉不敢诬一事于其间。视匹夫之见枉。若已推之。则其所以重其事而难慎之者。为如何哉。白沙之撰汉阴志文。皆以身经目睹者。备载无遗。先大监所撰碑文中。亦以为白沙之志。一事不遗云。而白沙于癸丑事。只书郑造,尹讱首发废母论。若我祖父当初出置之论其间情迹。或有毫发可疑。则以白沙刚直公正不遗一事之精鉴。有何容护之私。而独遗诛心一罪于衮钺之中。不为连书于二贼臣之下。如今碑文中所云也。愚伏郑公亦制汉阴状而同一其辞。苍石李公撰时翰从大父监司公墓碣。而特书曰。当造,讱发废母论时。公之兄某以持平持不可云云。此三贤者皆是当时同朝周旋。亲自目击。必能洞烛其心术隐微。若有奸情慝意。可加以诛心之法者。则以三公之贤。必不漏于特笔。而终不如此碑文中所书。抑独何欤。若使祖父出置之论。附会奸凶。真有杀弟之心。如郑桐溪之疏。则当其时。何不能致位清班。翱翔荣途。而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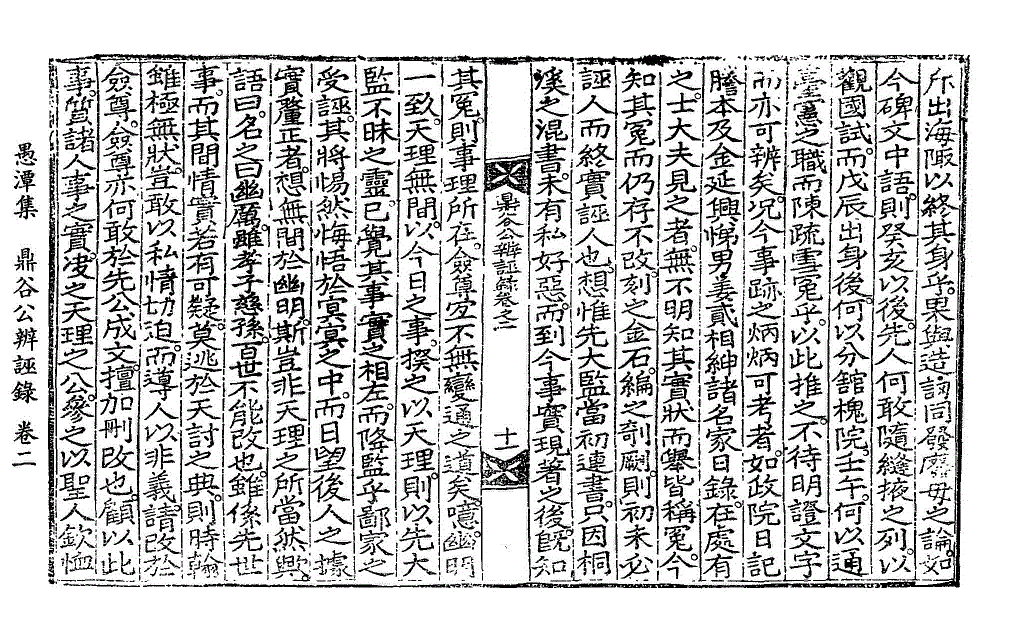 斥出海陬以终其身乎。果与造,讱同发废母之论。如今碑文中语。则癸亥以后。先人何敢随缝掖之列。以观国试。而戊辰出身后。何以分馆槐院。壬午。何以通台宪之职而陈疏雪冤乎。以此推之。不待明證文字而亦可辨矣。况今事迹之炳炳可考者。如政院日记誊本及金延兴悌男,姜贰相绅诸名家日录。在处有之。士大夫见之者。无不明知其实状而举皆称冤。今知其冤而仍存不改。刻之金石。编之剞劂。则初未必诬人而终实诬人也。想惟先大监当初连书。只因桐溪之混书。未有私好恶。而到今事实现著之后。既知其冤。则事理所在。佥尊宜不无变通之道矣。噫。幽明一致。天理无间。以今日之事。揆之以天理。则以先大监不昧之灵。已觉其事实之相左。而降监乎鄙家之受诬。其将惕然悔悟于冥冥之中。而日望后人之据实釐正者。想无间于幽明。斯岂非天理之所当然欤。语曰。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虽系先世事。而其间情实若有可疑。莫逃于天讨之典。则时翰虽极无状。岂敢以私情切迫。而导人以非义。请改于佥尊。佥尊亦何敢于先公成文。擅加删改也。顾以此事。质诸人事之实。决之天理之公。参之以圣人钦恤
斥出海陬以终其身乎。果与造,讱同发废母之论。如今碑文中语。则癸亥以后。先人何敢随缝掖之列。以观国试。而戊辰出身后。何以分馆槐院。壬午。何以通台宪之职而陈疏雪冤乎。以此推之。不待明證文字而亦可辨矣。况今事迹之炳炳可考者。如政院日记誊本及金延兴悌男,姜贰相绅诸名家日录。在处有之。士大夫见之者。无不明知其实状而举皆称冤。今知其冤而仍存不改。刻之金石。编之剞劂。则初未必诬人而终实诬人也。想惟先大监当初连书。只因桐溪之混书。未有私好恶。而到今事实现著之后。既知其冤。则事理所在。佥尊宜不无变通之道矣。噫。幽明一致。天理无间。以今日之事。揆之以天理。则以先大监不昧之灵。已觉其事实之相左。而降监乎鄙家之受诬。其将惕然悔悟于冥冥之中。而日望后人之据实釐正者。想无间于幽明。斯岂非天理之所当然欤。语曰。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虽系先世事。而其间情实若有可疑。莫逃于天讨之典。则时翰虽极无状。岂敢以私情切迫。而导人以非义。请改于佥尊。佥尊亦何敢于先公成文。擅加删改也。顾以此事。质诸人事之实。决之天理之公。参之以圣人钦恤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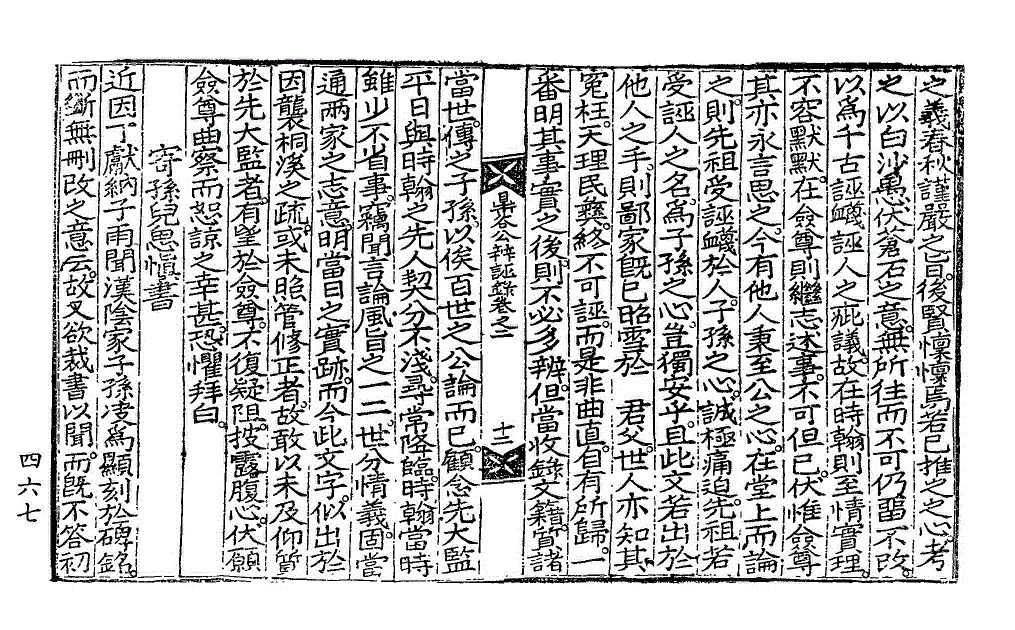 之义。春秋谨严之旨。后贤懔懔焉若己推之之心。考之以白沙,愚伏,苍石之意。无所往而不可仍留不改。以为千古诬蔑诬人之疵议。故在时翰则至情实理。不容默默。在佥尊则继志述事。不可但已。伏惟佥尊其亦永言思之。今有他人秉至公之心。在堂上而论之。则先祖受诬蔑于人。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若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且此文若出于他人之手。则鄙家既已昭雪于 君父。世人亦知其冤枉。天理民彝。终不可诬。而是非曲直。自有所归。一番明其事实之后。则不必多辨。但当收录文籍。质诸当世。传之子孙。以俟百世之公论而已。顾念先大监平日与时翰之先人契分不浅。寻常降临。时翰当时虽少不省事。窃闻言论风旨之一二。世分情义。固当通两家之志意。明当日之实迹。而今此文字。似出于因袭桐溪之疏。或未照管修正者。故敢以未及仰质于先大监者。有望于佥尊。不复疑阻。披露腹心。伏愿佥尊曲察而恕谅之幸甚。恐惧拜白。
之义。春秋谨严之旨。后贤懔懔焉若己推之之心。考之以白沙,愚伏,苍石之意。无所往而不可仍留不改。以为千古诬蔑诬人之疵议。故在时翰则至情实理。不容默默。在佥尊则继志述事。不可但已。伏惟佥尊其亦永言思之。今有他人秉至公之心。在堂上而论之。则先祖受诬蔑于人。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若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且此文若出于他人之手。则鄙家既已昭雪于 君父。世人亦知其冤枉。天理民彝。终不可诬。而是非曲直。自有所归。一番明其事实之后。则不必多辨。但当收录文籍。质诸当世。传之子孙。以俟百世之公论而已。顾念先大监平日与时翰之先人契分不浅。寻常降临。时翰当时虽少不省事。窃闻言论风旨之一二。世分情义。固当通两家之志意。明当日之实迹。而今此文字。似出于因袭桐溪之疏。或未照管修正者。故敢以未及仰质于先大监者。有望于佥尊。不复疑阻。披露腹心。伏愿佥尊曲察而恕谅之幸甚。恐惧拜白。寄孙儿思慎书
近因丁献纳子雨。闻汉阴家子孙决为显刻于碑铭。而断无删改之意云。故又欲裁书以闻。而既不答初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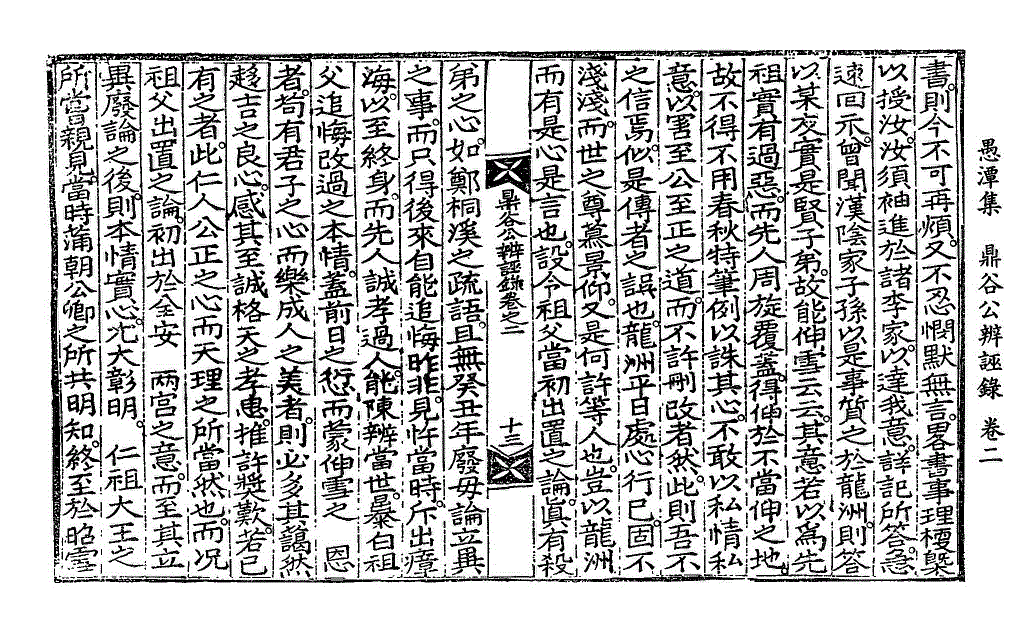 书。则今不可再烦。又不忍悯默无言。略书事理梗槩以授汝。汝须袖进于诸李家。以达我意。详记所答。急速回示。曾闻汉阴家子孙以是事质之于龙洲。则答以某友实是贤子弟。故能伸雪云云。其意若以为先祖实有过恶。而先人周旋覆盖。得伸于不当伸之地。故不得不用春秋特笔例以诛其心。不敢以私情私意。以害至公至正之道。而不许删改者然。此则吾不之信焉。似是传者之误也。龙洲平日处心行己。固不浅浅。而世之尊慕景仰。又是何许等人也。岂以龙洲而有是心是言也。设令祖父当初出置之论。真有杀弟之心。如郑桐溪之疏语。且无癸丑年废母论立异之事。而只得后来自能追悔昨非。见忤当时。斥出瘴海。以至终身。而先人诚孝过人。能陈辨当世。暴白祖父追悔改过之本情。盖前日之愆而蒙伸雪之 恩者。苟有君子之心而乐成人之美者。则必多其蔼然趋吉之良心。感其至诚格天之孝思。推许奖叹。若己有之者。此仁人公正之心而天理之所当然也。而况祖父出置之论。初出于全安 两宫之意。而至其立异废论之后。则本情实心。尤大彰明。 仁祖大王之所尝亲见。当时满朝公卿之所共明知。终至于昭雪
书。则今不可再烦。又不忍悯默无言。略书事理梗槩以授汝。汝须袖进于诸李家。以达我意。详记所答。急速回示。曾闻汉阴家子孙以是事质之于龙洲。则答以某友实是贤子弟。故能伸雪云云。其意若以为先祖实有过恶。而先人周旋覆盖。得伸于不当伸之地。故不得不用春秋特笔例以诛其心。不敢以私情私意。以害至公至正之道。而不许删改者然。此则吾不之信焉。似是传者之误也。龙洲平日处心行己。固不浅浅。而世之尊慕景仰。又是何许等人也。岂以龙洲而有是心是言也。设令祖父当初出置之论。真有杀弟之心。如郑桐溪之疏语。且无癸丑年废母论立异之事。而只得后来自能追悔昨非。见忤当时。斥出瘴海。以至终身。而先人诚孝过人。能陈辨当世。暴白祖父追悔改过之本情。盖前日之愆而蒙伸雪之 恩者。苟有君子之心而乐成人之美者。则必多其蔼然趋吉之良心。感其至诚格天之孝思。推许奖叹。若己有之者。此仁人公正之心而天理之所当然也。而况祖父出置之论。初出于全安 两宫之意。而至其立异废论之后。则本情实心。尤大彰明。 仁祖大王之所尝亲见。当时满朝公卿之所共明知。终至于昭雪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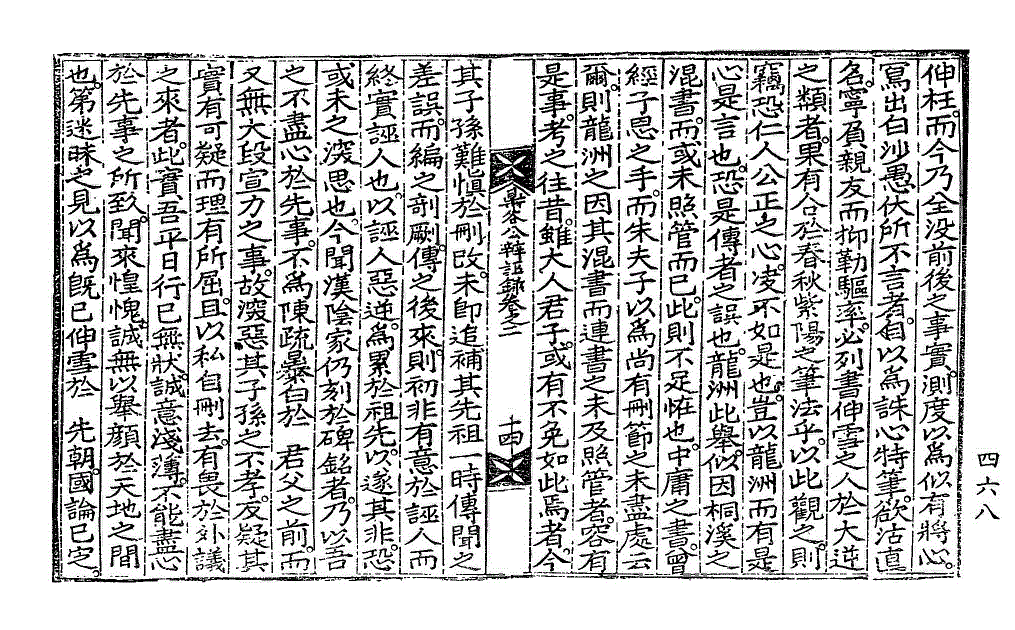 伸枉。而今乃全没前后之事实。测度以为似有将心。写出白沙,愚伏所不言者。自以为诛心特笔。欲沽直名。宁负亲友而抑勒驱率。必列书伸雪之人于大逆之类者。果有合于春秋紫阳之笔法乎。以此观之。则窃恐仁人公正之心。决不如是也。岂以龙洲而有是心是言也。恐是传者之误也。龙洲此举。似因桐溪之混书。而或未照管而已。此则不足怪也。中庸之书。曾经子思之手。而朱夫子以为尚有删节之未尽处云尔。则龙洲之因其混书而连书之未及照管者。容有是事。考之往昔。虽大人君子。或有不免如此焉者。今其子孙难慎于删改。未即追补其先祖一时传闻之差误。而编之剞劂。传之后来。则初非有意于诬人而终实诬人也。以诬人恶逆。为累于祖先。以遂其非。恐或未之深思也。今闻汉阴家仍刻于碑铭者。乃以吾之不尽心于先事。不为陈疏暴白于 君父之前。而又无大段宣力之事。故深恶其子孙之不孝。反疑其实有可疑而理有所屈。且以私自删去。有畏于外议之来者。此实吾平日行己无状。诚意浅薄。不能尽心于先事之所致。闻来惶愧。诚无以举颜于天地之间也。第迷昧之见以为既已伸雪于 先朝。国论已定。
伸枉。而今乃全没前后之事实。测度以为似有将心。写出白沙,愚伏所不言者。自以为诛心特笔。欲沽直名。宁负亲友而抑勒驱率。必列书伸雪之人于大逆之类者。果有合于春秋紫阳之笔法乎。以此观之。则窃恐仁人公正之心。决不如是也。岂以龙洲而有是心是言也。恐是传者之误也。龙洲此举。似因桐溪之混书。而或未照管而已。此则不足怪也。中庸之书。曾经子思之手。而朱夫子以为尚有删节之未尽处云尔。则龙洲之因其混书而连书之未及照管者。容有是事。考之往昔。虽大人君子。或有不免如此焉者。今其子孙难慎于删改。未即追补其先祖一时传闻之差误。而编之剞劂。传之后来。则初非有意于诬人而终实诬人也。以诬人恶逆。为累于祖先。以遂其非。恐或未之深思也。今闻汉阴家仍刻于碑铭者。乃以吾之不尽心于先事。不为陈疏暴白于 君父之前。而又无大段宣力之事。故深恶其子孙之不孝。反疑其实有可疑而理有所屈。且以私自删去。有畏于外议之来者。此实吾平日行己无状。诚意浅薄。不能尽心于先事之所致。闻来惶愧。诚无以举颜于天地之间也。第迷昧之见以为既已伸雪于 先朝。国论已定。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9H 页
 则今以一人袭谬文字之故。更为告讦。请伸既伸之事于 君父之前者。实无意义。今请更伸而后。或又有如此之事。则亦可以每每请伸乎。反覆思量。有违事理。终有所不敢焉。且彼既谓之直笔而用贲先墓。则虽有 君命。似难轻改。若知其诬蔑。则子孙孝敬之心。自不敢以诬人之辞。玷累于其先祖之墓道。必不肯为人而不为己。为己而不为先。自能尽其诚孝。以定取舍者。此乃人之常情也。盖吾家所遭。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而既已昭雪。内省不疚。今此龙洲之袭谬混书者。以事理论之。则毕竟是横逆之来。天理民彝终不可诬。而是非曲直。自有所归。今若不堪吾痛迫之私情。一向奔走从臾而请改焉。则是无异于直不在我而求直于彼者。岂可更容一毫私智私意。周旋其间。有若阴祈而曲图者然哉。故乃以明證文字及书札。论其事理之是非。使儿辈进陈于汉阴子孙。而恭俟可否矣。不自意直以此不孝无状。而不赐答书。断欲必刻。终未闻有改图之意。此则由我无良。累及先祖。直欲求死而不可得也。然此事只观事之是非理之当否而已。若事理不可改。则岂以受诬之家奔走周旋。而遽为之改。事理可以改。则自可往复
则今以一人袭谬文字之故。更为告讦。请伸既伸之事于 君父之前者。实无意义。今请更伸而后。或又有如此之事。则亦可以每每请伸乎。反覆思量。有违事理。终有所不敢焉。且彼既谓之直笔而用贲先墓。则虽有 君命。似难轻改。若知其诬蔑。则子孙孝敬之心。自不敢以诬人之辞。玷累于其先祖之墓道。必不肯为人而不为己。为己而不为先。自能尽其诚孝。以定取舍者。此乃人之常情也。盖吾家所遭。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而既已昭雪。内省不疚。今此龙洲之袭谬混书者。以事理论之。则毕竟是横逆之来。天理民彝终不可诬。而是非曲直。自有所归。今若不堪吾痛迫之私情。一向奔走从臾而请改焉。则是无异于直不在我而求直于彼者。岂可更容一毫私智私意。周旋其间。有若阴祈而曲图者然哉。故乃以明證文字及书札。论其事理之是非。使儿辈进陈于汉阴子孙。而恭俟可否矣。不自意直以此不孝无状。而不赐答书。断欲必刻。终未闻有改图之意。此则由我无良。累及先祖。直欲求死而不可得也。然此事只观事之是非理之当否而已。若事理不可改。则岂以受诬之家奔走周旋。而遽为之改。事理可以改。则自可往复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69L 页
 商确。以求至当之归而后已。奚可以受诬家子孙之不急急尽力。诿以自屈。而遽书于恶逆之列而不少疑也。明證文字。如彼其炳炳可考。而只畏世之不知者之或有谤议。明知其诬人爽实之辞。而断然不顾。显刻于先祖之墓道。岂但为吾家之诬蔑。在彼自尽诚敬一毫无憾之道。亦未知其果合于宜也。须以此意奉质事理。以听裁处。
商确。以求至当之归而后已。奚可以受诬家子孙之不急急尽力。诿以自屈。而遽书于恶逆之列而不少疑也。明證文字。如彼其炳炳可考。而只畏世之不知者之或有谤议。明知其诬人爽实之辞。而断然不顾。显刻于先祖之墓道。岂但为吾家之诬蔑。在彼自尽诚敬一毫无憾之道。亦未知其果合于宜也。须以此意奉质事理。以听裁处。李参奉(后晟)。与赵牙山(九辂),司书(九畹)书。
晟白。上年冬间。豚儿持丁进善时翰氏抵佥侍前书来。晟于老病无聊中偶然看过。丁公为其先祖讼冤之事。极其痛迫。而晟以后生。不详昏朝时事。况汉阴相国碑文。又是龙洲先生手撰。则必据实记出。实非议论敢到处也。丁公书虽多分疏文字。亦看过而已。其后豚儿偶得梧里相国日记来。从首至尾。屡次翻阅。则癸丑年郑桐溪疏。果有郑造,尹讱,丁好宽等首发废母杀弟之论云云。龙洲先生之撰述。必本于此疏。而至乙卯年 母后各处之论。持平丁好宽与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立异之说。昭昭不可掩。其后台启及儒疏中。只举郑造,尹讱,李伟卿等首倡废母之论云。绝无丁好宽名字。则丁公书所谓只论大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0H 页
 君出置之事。而不与于废母论云者。必无疑也。郑桐溪既在北道任所。必不详当时颠末。只据传闻或朝报出置大君之说。不甚照管而混同言及耶。龙洲先生亦于其时尚在布衣。或远居居昌等地。于 朝家事。亦不得一一目睹。撰述碑文时。只据桐溪疏而有此云云耶。皆未可臆料也。桐溪之疏。若以废母杀弟之论。岐而二之。各指其人。则后之观者。可以立辨。而今既连书三人名。而曰首发废母杀弟之论云云。其不审指意之各有所归。而致人混见者。良以此也。第桐溪忠言直节。在今古一人而已。则今谓桐溪疏有误下文字云。实涉僭猥。而癸丑乙卯间。 朝家记实文字。历历可考。则岂曰桐溪疏。而不敢云云乎。况梧里相国日记誊书当时台启。无一字加减。其中有曰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启曰云云。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所敢议乎云云。今日合司席上。有以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云云。此三人所启。与他台启颇直截。无含糊底意思。此可见三公所蕴矣。于此可见丁好宽于癸丑避嫌时。只论出置大君。而不预于废母论。的然可知也。第梧里癸丑日记中不书台启。故不得记出当时事实。可慨也。其日持
君出置之事。而不与于废母论云者。必无疑也。郑桐溪既在北道任所。必不详当时颠末。只据传闻或朝报出置大君之说。不甚照管而混同言及耶。龙洲先生亦于其时尚在布衣。或远居居昌等地。于 朝家事。亦不得一一目睹。撰述碑文时。只据桐溪疏而有此云云耶。皆未可臆料也。桐溪之疏。若以废母杀弟之论。岐而二之。各指其人。则后之观者。可以立辨。而今既连书三人名。而曰首发废母杀弟之论云云。其不审指意之各有所归。而致人混见者。良以此也。第桐溪忠言直节。在今古一人而已。则今谓桐溪疏有误下文字云。实涉僭猥。而癸丑乙卯间。 朝家记实文字。历历可考。则岂曰桐溪疏。而不敢云云乎。况梧里相国日记誊书当时台启。无一字加减。其中有曰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启曰云云。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所敢议乎云云。今日合司席上。有以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云云。此三人所启。与他台启颇直截。无含糊底意思。此可见三公所蕴矣。于此可见丁好宽于癸丑避嫌时。只论出置大君。而不预于废母论。的然可知也。第梧里癸丑日记中不书台启。故不得记出当时事实。可慨也。其日持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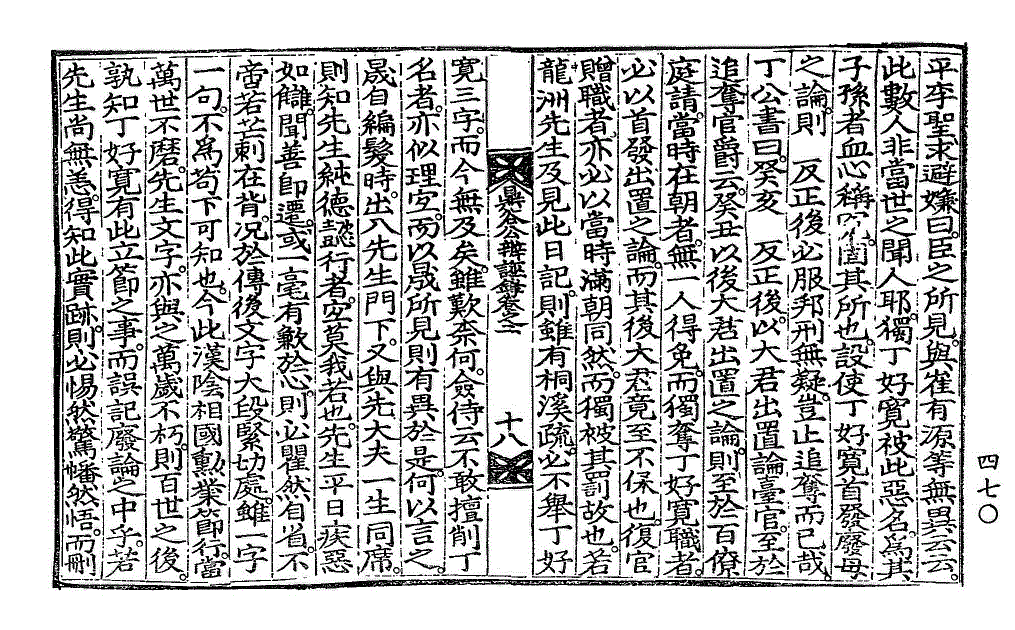 平李圣求避嫌曰。臣之所见。与崔有源等无异云云。此数人非当世之闻人耶。独丁好宽被此恶名。为其子孙者血心称冤。固其所也。设使丁好宽首发废母之论。则 反正后必服邦刑无疑。岂止追夺而已哉。丁公书曰。癸亥 反正后。以大君出置论台官。至于追夺官爵云。癸丑以后大君出置之论。则至于百僚庭请。当时在朝者。无一人得免。而独夺丁好宽职者。必以首发出置之论。而其后大君竟至不保也。复官赠职者。亦必以当时满朝同然。而独被其罚故也。若龙洲先生及见此日记。则虽有桐溪疏。必不举丁好宽三字。而今无及矣。虽叹柰何。佥侍云不敢擅削丁名者。亦似理宜。而以晟所见则有异于是。何以言之。晟自编发时。出入先生门下。又与先大夫一生同席。则知先生纯德懿行者。宜莫我若也。先生平日疾恶如雠。闻善即迁。或一毫有歉于心。则必瞿然自省。不啻若芒刺在背。况于传后文字大段紧切处。虽一字一句。不为苟下可知也。今此汉阴相国勋业节行。当万世不磨。先生文字。亦与之万岁不朽。则百世之后。孰知丁好宽有此立节之事。而误记废论之中乎。若先生尚无恙。得知此实迹。则必惕然惊幡然悟。而删
平李圣求避嫌曰。臣之所见。与崔有源等无异云云。此数人非当世之闻人耶。独丁好宽被此恶名。为其子孙者血心称冤。固其所也。设使丁好宽首发废母之论。则 反正后必服邦刑无疑。岂止追夺而已哉。丁公书曰。癸亥 反正后。以大君出置论台官。至于追夺官爵云。癸丑以后大君出置之论。则至于百僚庭请。当时在朝者。无一人得免。而独夺丁好宽职者。必以首发出置之论。而其后大君竟至不保也。复官赠职者。亦必以当时满朝同然。而独被其罚故也。若龙洲先生及见此日记。则虽有桐溪疏。必不举丁好宽三字。而今无及矣。虽叹柰何。佥侍云不敢擅削丁名者。亦似理宜。而以晟所见则有异于是。何以言之。晟自编发时。出入先生门下。又与先大夫一生同席。则知先生纯德懿行者。宜莫我若也。先生平日疾恶如雠。闻善即迁。或一毫有歉于心。则必瞿然自省。不啻若芒刺在背。况于传后文字大段紧切处。虽一字一句。不为苟下可知也。今此汉阴相国勋业节行。当万世不磨。先生文字。亦与之万岁不朽。则百世之后。孰知丁好宽有此立节之事。而误记废论之中乎。若先生尚无恙。得知此实迹。则必惕然惊幡然悟。而删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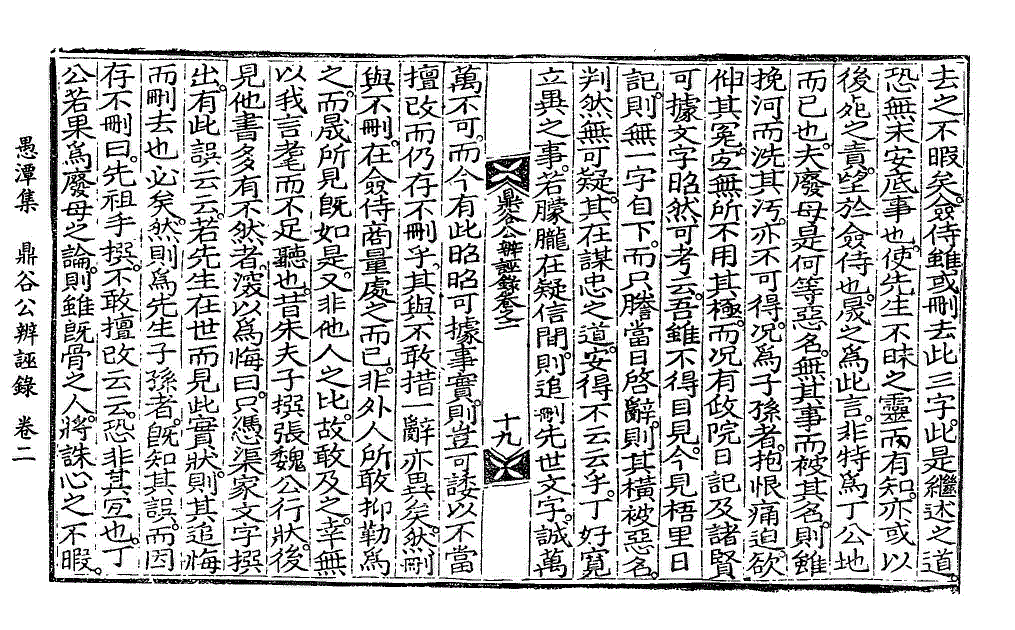 去之不暇矣。佥侍虽或删去此三字。此是继述之道。恐无未安底事也。使先生不昧之灵而有知。亦或以后死之责。望于佥侍也。晟之为此言。非特为丁公地而已也。夫废母是何等恶名。无其事而被其名。则虽挽河而洗其污。亦不可得。况为子孙者。抱恨痛迫。欲伸其冤。宜无所不用其极。而况有政院日记及诸贤可据文字昭然可考云。吾虽不得目见。今见梧里日记。则无一字自下。而只誊当日启辞。则其横被恶名。判然无可疑。其在谋忠之道。安得不云云乎。丁好宽立异之事。若䑃胧在疑信间。则追删先世文字。诚万万不可。而今有此昭昭可据事实。则岂可诿以不当擅改而仍存不删乎。其与不敢措一辞亦异矣。然删与不删。在佥侍商量处之而已。非外人所敢抑勒为之。而晟所见既如是。又非他人之比。故敢及之。幸无以我言耄而不足听也。昔朱夫子撰张魏公行状。后见他书多有不然者。深以为悔曰。只凭渠家文字撰出。有此误云云。若先生在世而见此实状。则其追悔而删去也必矣。然则为先生子孙者。既知其误。而因存不删曰。先祖手撰。不敢擅改云云。恐非其宜也。丁公若果为废母之论。则虽既骨之人。将诛心之不暇。
去之不暇矣。佥侍虽或删去此三字。此是继述之道。恐无未安底事也。使先生不昧之灵而有知。亦或以后死之责。望于佥侍也。晟之为此言。非特为丁公地而已也。夫废母是何等恶名。无其事而被其名。则虽挽河而洗其污。亦不可得。况为子孙者。抱恨痛迫。欲伸其冤。宜无所不用其极。而况有政院日记及诸贤可据文字昭然可考云。吾虽不得目见。今见梧里日记。则无一字自下。而只誊当日启辞。则其横被恶名。判然无可疑。其在谋忠之道。安得不云云乎。丁好宽立异之事。若䑃胧在疑信间。则追删先世文字。诚万万不可。而今有此昭昭可据事实。则岂可诿以不当擅改而仍存不删乎。其与不敢措一辞亦异矣。然删与不删。在佥侍商量处之而已。非外人所敢抑勒为之。而晟所见既如是。又非他人之比。故敢及之。幸无以我言耄而不足听也。昔朱夫子撰张魏公行状。后见他书多有不然者。深以为悔曰。只凭渠家文字撰出。有此误云云。若先生在世而见此实状。则其追悔而删去也必矣。然则为先生子孙者。既知其误。而因存不删曰。先祖手撰。不敢擅改云云。恐非其宜也。丁公若果为废母之论。则虽既骨之人。将诛心之不暇。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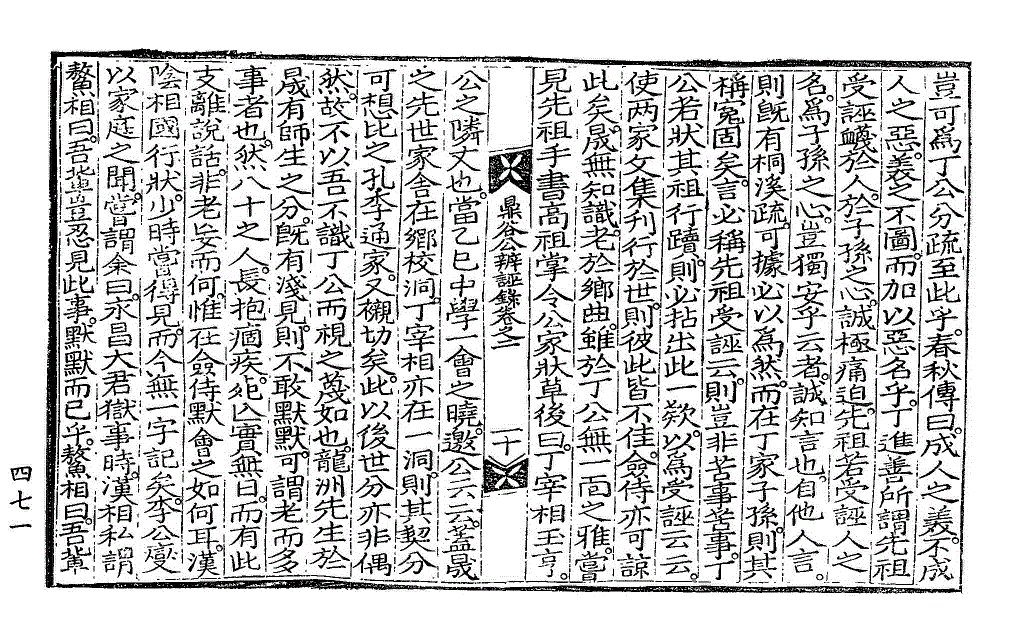 岂可为丁公分疏至此乎。春秋传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美之不图。而加以恶名乎。丁进善所谓先祖受诬蔑于人。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若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云者。诚知言也。自他人言。则既有桐溪疏。可据必以为然。而在丁家子孙。则其称冤固矣。言必称先祖受诬云。则岂非苦事苦事。丁公若状其祖行迹。则必拈出此一款。以为受诬云云。使两家文集刊行于世。则彼此皆不佳。佥侍亦可谅此矣。晟无知识。老于乡曲。虽于丁公无一面之雅。尝见先祖手书高祖掌令公家状草后曰。丁宰相玉亨。公之邻丈也。当乙巳中学一会之晓。邀公云云。盖晟之先世家舍在乡校洞。丁宰相亦在一洞。则其契分可想比之孔,李通家。又衬切矣。此以后世分亦非偶然。故不以吾不识丁公而视之蔑如也。龙洲先生于晟有师生之分。既有浅见。则不敢默默。可谓老而多事者也。然八十之人。长抱痼疾。死亡实无日。而有此支离说话。非老妄而何。惟在佥侍默会之如何耳。汉阴相国行状。少时尝得见。而今无一字记矣。李公燮以家庭之闻。尝谓余曰。永昌大君狱事时。汉相私谓鳌相曰。吾辈岂忍见此事。默默而已乎。鳌相曰。吾辈
岂可为丁公分疏至此乎。春秋传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美之不图。而加以恶名乎。丁进善所谓先祖受诬蔑于人。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若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云者。诚知言也。自他人言。则既有桐溪疏。可据必以为然。而在丁家子孙。则其称冤固矣。言必称先祖受诬云。则岂非苦事苦事。丁公若状其祖行迹。则必拈出此一款。以为受诬云云。使两家文集刊行于世。则彼此皆不佳。佥侍亦可谅此矣。晟无知识。老于乡曲。虽于丁公无一面之雅。尝见先祖手书高祖掌令公家状草后曰。丁宰相玉亨。公之邻丈也。当乙巳中学一会之晓。邀公云云。盖晟之先世家舍在乡校洞。丁宰相亦在一洞。则其契分可想比之孔,李通家。又衬切矣。此以后世分亦非偶然。故不以吾不识丁公而视之蔑如也。龙洲先生于晟有师生之分。既有浅见。则不敢默默。可谓老而多事者也。然八十之人。长抱痼疾。死亡实无日。而有此支离说话。非老妄而何。惟在佥侍默会之如何耳。汉阴相国行状。少时尝得见。而今无一字记矣。李公燮以家庭之闻。尝谓余曰。永昌大君狱事时。汉相私谓鳌相曰。吾辈岂忍见此事。默默而已乎。鳌相曰。吾辈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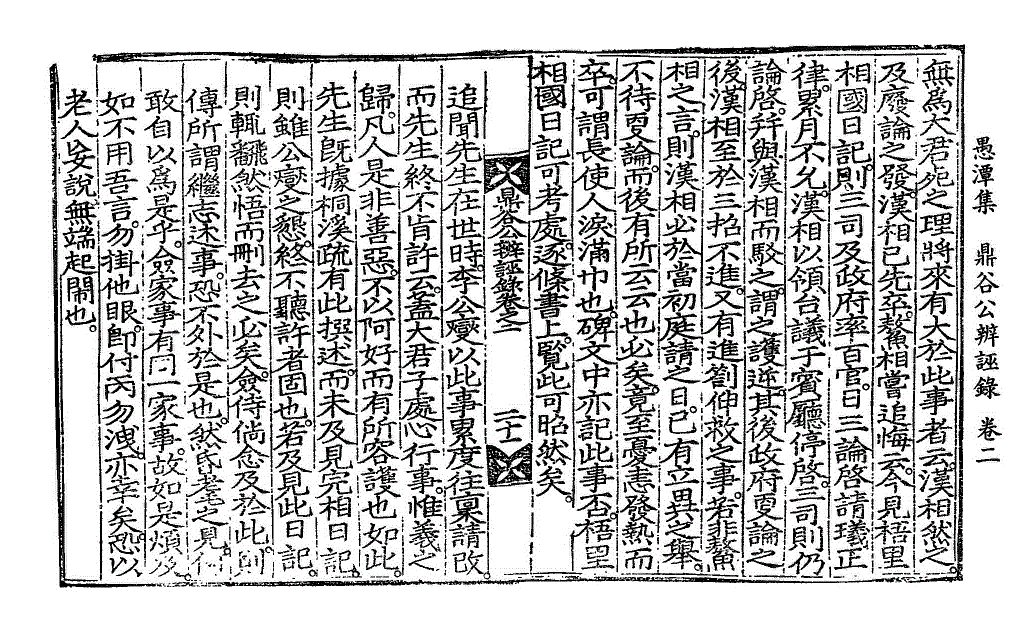 无为大君死之理将来有大于此事者云。汉相然之。及废论之发。汉相已先卒。鳌相尝追悔云。今见梧里相国日记。则三司及政府率百官。日三论启请㼁正律。累月不允。汉相以领台议于宾厅停启。三司则仍论启。拜与汉相而驳之。谓之护逆。其后政府更论之后。汉相至于三招不进。又有进劄伸救之事。若非鳌相之言。则汉相必于当初庭请之日。已有立异之举。不待更论。而后有所云云也必矣。竟至忧恚发热而卒。可谓长使人泪满巾也。碑文中亦记此事否。梧里相国日记可考处。逐条书上。览此可昭然矣。
无为大君死之理将来有大于此事者云。汉相然之。及废论之发。汉相已先卒。鳌相尝追悔云。今见梧里相国日记。则三司及政府率百官。日三论启请㼁正律。累月不允。汉相以领台议于宾厅停启。三司则仍论启。拜与汉相而驳之。谓之护逆。其后政府更论之后。汉相至于三招不进。又有进劄伸救之事。若非鳌相之言。则汉相必于当初庭请之日。已有立异之举。不待更论。而后有所云云也必矣。竟至忧恚发热而卒。可谓长使人泪满巾也。碑文中亦记此事否。梧里相国日记可考处。逐条书上。览此可昭然矣。[识(丁时翰)]
追闻先生在世时。李公燮以此事累度往禀请改。而先生终不肯许云。盖大君子处心行事。惟义之归。凡人是非善恶。不以阿好而有所容护也如此。先生既据桐溪疏有此撰述。而未及见完相日记。则虽公燮之恳。终不听许者固也。若及见此日记。则辄翻然悟而删去之必矣。佥侍倘念及于此。则传所谓继志述事。恐不外于是也。然昏耄之见。何敢自以为是乎。佥家事有同一家事。故如是烦及。如不用吾言。勿挂他眼。即付丙勿泄。亦幸矣。恐以老人妄说。无端起闹也。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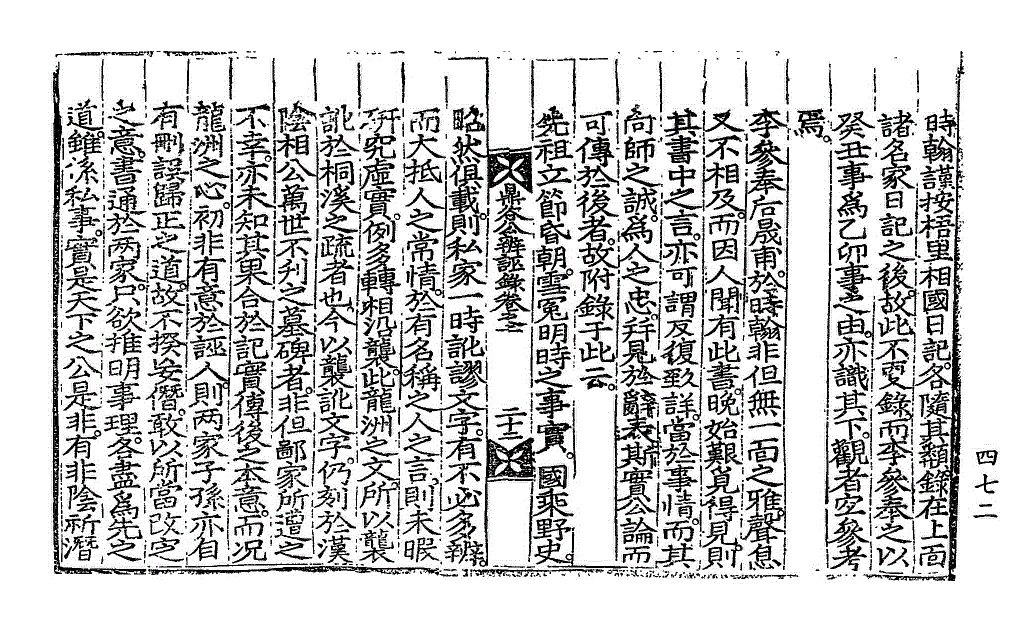 时翰谨按梧里相国日记。各随其类。录在上面诸名家日记之后。故此不更录。而李参奉之以癸丑事为乙卯事之由。亦识其下。观者宜参考焉。
时翰谨按梧里相国日记。各随其类。录在上面诸名家日记之后。故此不更录。而李参奉之以癸丑事为乙卯事之由。亦识其下。观者宜参考焉。李参奉后晟甫。于时翰非但无一面之雅。声息又不相及。而因人闻有此书。晚始艰觅得见。则其书中之言。亦可谓反复致详。当于事情。而其向师之诚。为人之忠。并见于辞表。斯实公论而可传于后者。故附录于此云。
先祖立节昏朝。雪冤明时之事实。 国乘野史。昭然俱载。则私家一时讹谬文字。有不必多辨。而大抵人之常情。于有名称之人之言。则未暇研究虚实。例多转相沿袭。此龙洲之文。所以袭讹于桐溪之疏者也。今以袭讹文字。仍刻于汉阴相公万世不刊之墓碑者。非但鄙家所遭之不幸。亦未知其果合于记实传后之本意。而况龙洲之心。初非有意于诬人。则两家子孙亦自有删误归正之道。故不揆妄僭。敢以所当改定之意。书通于两家。只欲推明事理。各尽为先之道。虽系私事。实是天下之公是非。有非阴祈潜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3H 页
 嘱之比。而侧听累岁不见其有所反复。莫非不肖孙不孝无状。行不孚人之致。反躬自讼之馀。聊此裒辑诸名家日录及伸冤文字,辨论书札。合为一册。名之曰辨诬录。欲以质诸当世之君子。世之君子倘赐一览。则其时事实。自可瞭然。而亦可验不肖孙辨质之言不至无稽也。愿得明白辨论之题跋语。藏诸巾笥。以遗子孙云尔。岁丙子季秋。不肖孙时翰谨识。
嘱之比。而侧听累岁不见其有所反复。莫非不肖孙不孝无状。行不孚人之致。反躬自讼之馀。聊此裒辑诸名家日录及伸冤文字,辨论书札。合为一册。名之曰辨诬录。欲以质诸当世之君子。世之君子倘赐一览。则其时事实。自可瞭然。而亦可验不肖孙辨质之言不至无稽也。愿得明白辨论之题跋语。藏诸巾笥。以遗子孙云尔。岁丙子季秋。不肖孙时翰谨识。丁氏辨诬录后语
甚矣。人之所见之不一也。凡义理肯綮之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则有之矣。至于已然之迹。其善恶邪正。不可得以低仰者。犹且是非互出。予夺各立。亦独何哉。故知兴海郡事罗州丁公立朝末年。当光海昏乱。是时大奸擅弄于上。群小怂恿于下。倡为不道之说。以乱伦纪。一言从违之间。祸福立至。苟非平日所见之正所守之确。未有不少为渐染。而公能与二三正士。挺立抗议。屹然为颓波之砥柱。使邪说者有所畏忌。何其伟哉。及 仁庙反正之后。特命褒录当时立节之士。生者加资。死者 赠爵。泽及幽明。 恩典大霈。而政院以公尝与于永昌大君出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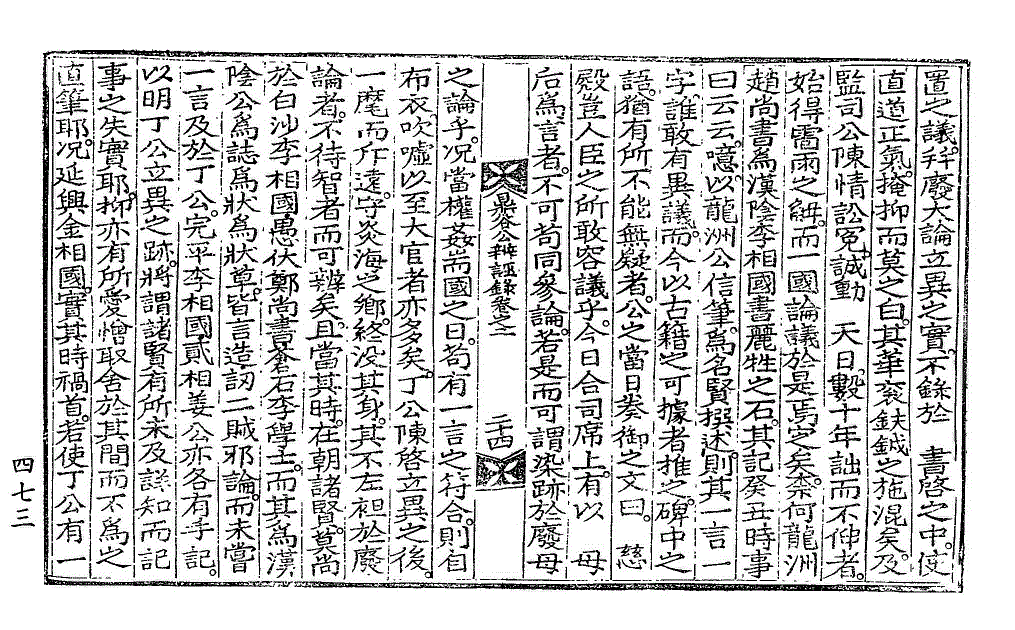 置之议。并废大论立异之实。不录于 书启之中。使直道正气。掩抑而莫之白。其华衮鈇钺之施混矣。及监司公陈情讼冤。诚动 天日。数十年诎而不伸者。始得雷雨之解。而一国论议于是焉定矣。柰何龙洲赵尚书为汉阴李相国书丽牲之石。其记癸丑时事曰云云。噫。以龙洲公信笔。为名贤撰述。则其一言一字。谁敢有异议。而今以古籍之可据者推之。碑中之语。犹有所不能无疑者。公之当日奏御之文曰。 慈殿岂人臣之所敢容议乎。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若是而可谓染迹于废母之论乎。况当权奸耑国之日。苟有一言之符合。则自布衣。吹嘘以至大官者亦多矣。丁公陈启立异之后。一麾而斥远。守炎海之乡。终没其身。其不左袒于废论者。不待智者而可辨矣。且当其时。在朝诸贤。莫尚于白沙李相国,愚伏郑尚书,苍石李学士。而其为汉阴公为志为状为状草。皆言造,讱二贼邪论。而未尝一言及于丁公。完平李相国,贰相姜公亦各有手记。以明丁公立异之迹。将谓诸贤有所未及详知而记事之失实耶。抑亦有所爱憎取舍于其间而不为之直笔耶。况延兴金相国。实其时祸首。若使丁公有一
置之议。并废大论立异之实。不录于 书启之中。使直道正气。掩抑而莫之白。其华衮鈇钺之施混矣。及监司公陈情讼冤。诚动 天日。数十年诎而不伸者。始得雷雨之解。而一国论议于是焉定矣。柰何龙洲赵尚书为汉阴李相国书丽牲之石。其记癸丑时事曰云云。噫。以龙洲公信笔。为名贤撰述。则其一言一字。谁敢有异议。而今以古籍之可据者推之。碑中之语。犹有所不能无疑者。公之当日奏御之文曰。 慈殿岂人臣之所敢容议乎。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若是而可谓染迹于废母之论乎。况当权奸耑国之日。苟有一言之符合。则自布衣。吹嘘以至大官者亦多矣。丁公陈启立异之后。一麾而斥远。守炎海之乡。终没其身。其不左袒于废论者。不待智者而可辨矣。且当其时。在朝诸贤。莫尚于白沙李相国,愚伏郑尚书,苍石李学士。而其为汉阴公为志为状为状草。皆言造,讱二贼邪论。而未尝一言及于丁公。完平李相国,贰相姜公亦各有手记。以明丁公立异之迹。将谓诸贤有所未及详知而记事之失实耶。抑亦有所爱憎取舍于其间而不为之直笔耶。况延兴金相国。实其时祸首。若使丁公有一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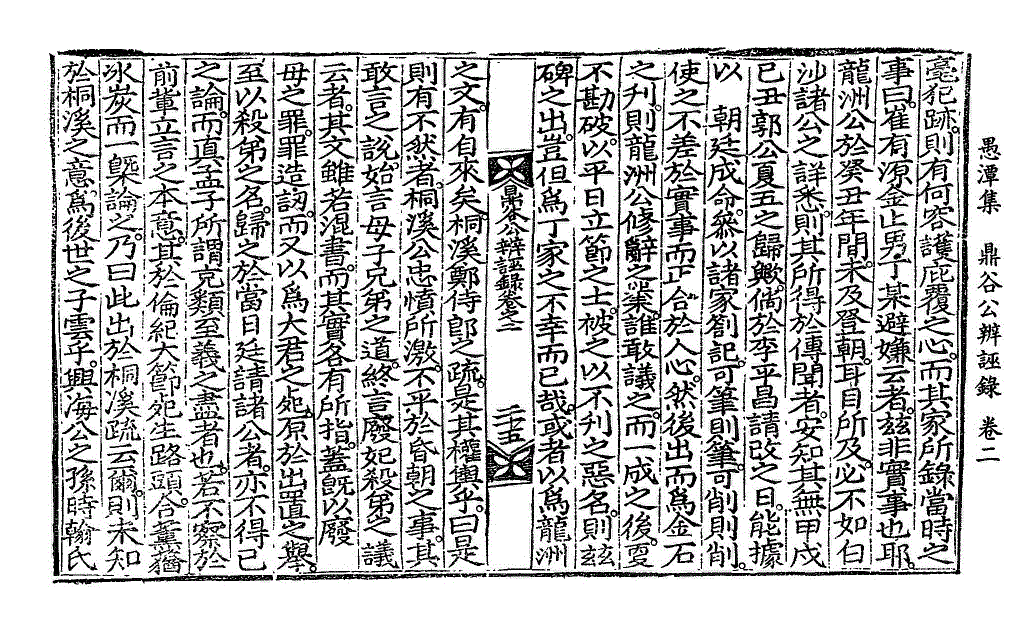 毫犯迹。则有何容护庇覆之心。而其家所录当时之事曰。崔有源,金止男,丁某避嫌云者。玆非实事也耶。龙洲公于癸丑年间。未及登朝。耳目所及。必不如白沙诸公之详悉。则其所得于传闻者。安知其无甲戌己丑郭公夏五之归欤。倘于李平昌请改之日。能据以 朝廷成命。参以诸家劄记。可笔则笔。可削则削。使之不差于实事而正合于人心。然后出而为金石之刊。则龙洲公修辞之业。谁敢议之。而一成之后。更不勘破。以平日立节之士。被之以不刊之恶名。则玆碑之出。岂但为丁家之不幸而已哉。或者以为龙洲之文。有自来矣。桐溪郑侍郎之疏。是其权舆乎。曰是则有不然者。桐溪公忠愤所激。不平于昏朝之事。其敢言之说。始言母子兄弟之道。终言废妃杀弟之议云者。其文虽若混书。而其实各有所指。盖既以废 母之罪。罪造,讱。而又以为大君之死。原于出置之举。至以杀弟之名。归之于当日廷请诸公者。亦不得已之论。而真孟子所谓克类至义之尽者也。若不察于前辈立言之本意。其于伦纪大节死生路头。合薰莸冰炭而一槩论之。乃曰此出于桐溪疏云尔。则未知于桐溪之意。为后世之子云乎。兴海公之孙时翰氏
毫犯迹。则有何容护庇覆之心。而其家所录当时之事曰。崔有源,金止男,丁某避嫌云者。玆非实事也耶。龙洲公于癸丑年间。未及登朝。耳目所及。必不如白沙诸公之详悉。则其所得于传闻者。安知其无甲戌己丑郭公夏五之归欤。倘于李平昌请改之日。能据以 朝廷成命。参以诸家劄记。可笔则笔。可削则削。使之不差于实事而正合于人心。然后出而为金石之刊。则龙洲公修辞之业。谁敢议之。而一成之后。更不勘破。以平日立节之士。被之以不刊之恶名。则玆碑之出。岂但为丁家之不幸而已哉。或者以为龙洲之文。有自来矣。桐溪郑侍郎之疏。是其权舆乎。曰是则有不然者。桐溪公忠愤所激。不平于昏朝之事。其敢言之说。始言母子兄弟之道。终言废妃杀弟之议云者。其文虽若混书。而其实各有所指。盖既以废 母之罪。罪造,讱。而又以为大君之死。原于出置之举。至以杀弟之名。归之于当日廷请诸公者。亦不得已之论。而真孟子所谓克类至义之尽者也。若不察于前辈立言之本意。其于伦纪大节死生路头。合薰莸冰炭而一槩论之。乃曰此出于桐溪疏云尔。则未知于桐溪之意。为后世之子云乎。兴海公之孙时翰氏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4L 页
 肥遁 明时。累徵不起。不屑于世间荣辱。而犹以其先代枉被不韪之语为至痛。乃裒集诸名家日录及监司公沥血之疏。与其近日往复简牍为一帙。使后来见之者。瞭然于是非之辨。惟樟忝从徵士游。颇得其事之颠末。窃自慨然曰。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圣人之于善善无所苟如此。则况于以不善之名。加之于不当加之地乎。龙洲赵尚书以近代名卿。为节义之所宗。而纂言之际。卒未免为后人之起疑。使丁氏子孙不得不有所分疏。噫。乙亥仲夏。宣城李惟樟谨识。
肥遁 明时。累徵不起。不屑于世间荣辱。而犹以其先代枉被不韪之语为至痛。乃裒集诸名家日录及监司公沥血之疏。与其近日往复简牍为一帙。使后来见之者。瞭然于是非之辨。惟樟忝从徵士游。颇得其事之颠末。窃自慨然曰。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圣人之于善善无所苟如此。则况于以不善之名。加之于不当加之地乎。龙洲赵尚书以近代名卿。为节义之所宗。而纂言之际。卒未免为后人之起疑。使丁氏子孙不得不有所分疏。噫。乙亥仲夏。宣城李惟樟谨识。书丁大夫辨诬录后
记昏朝癸丑年事
梧里李相国,姜贰相绅日录及金延兴悌男家藏日记。俱载政院日记。书当日事颇详。三家所录。大略相同。可谓惇史矣。其录曰。万历癸丑五月二十五日。掌令郑造,尹讱 启辞。辞意绝悖。献纳柳活,正言朴弘道依违其议。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等立异。(其避嫌 启辞略云。金悌男凶谋逆状。孰不痛心。而至于 慈殿。岂人臣所敢言。惟 殿下考古圣人处置之得宜者行之无愧于心。然后可免后世之讥矣。人臣事君。纳君于无过之地。是第一义。臣等于今日合司席上。言及 母后之议。不敢苟同。请递臣职。大司谏李志完避辞。与崔有源等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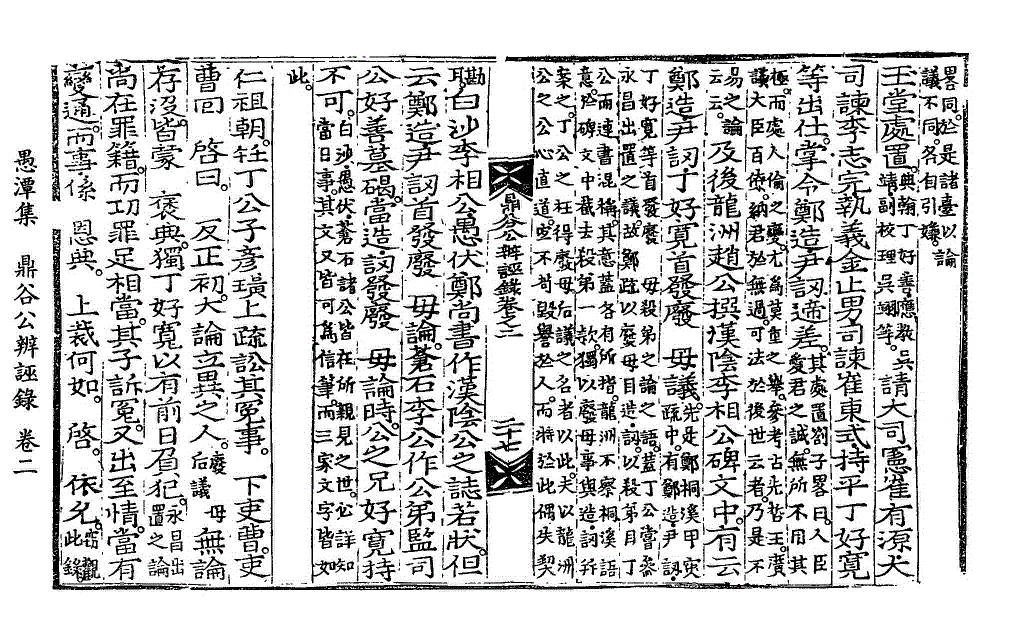 略同。于是诸台以论议不同。各自引嫌。)
略同。于是诸台以论议不同。各自引嫌。)玉堂处置。(典翰丁好善,应教吴靖,副校理吴翊等。)请大司宪崔有源,大司谏李志完,执义金止男,司谏崔东式,持平丁好宽等出仕。掌令郑造,尹讱递差。(其处置劄子略曰。人臣爱君之诚。无所不用其极。而处人伦之变。尤为莫重之举。参考古先哲王。广议大臣百僚。纳君于无过。可法于后世云者。乃是不易之论云云。)及后龙洲赵公撰汉阴李相公碑文中。有云郑造,尹讱,丁好宽首发废 母议。(先是郑桐溪甲寅疏中。有郑造,尹讱,丁好宽等首发废 母杀弟之论之语。盖丁公尝参永昌出置之议。故郑疏以废母目造,讱。以杀弟目丁公而连书混称。其意盖各有所指。龙洲不察桐溪语意。于碑文中截去杀弟一款。独以废母事与造,讱并案之。丁公之枉得废母后议之名者以此。夫以龙洲公之公心直道。宜不苟毁誉于人。而特于此偶失契勘耳。)白沙李相公,愚伏郑尚书作汉阴公之志若状。但云郑造,尹讱首发废 母论。苍石李公作公弟监司公好善墓碣。当造,讱发废 母论时。公之兄好宽持不可。(白沙,愚伏,苍石诸公皆在所亲见之世。必详知当日事。其文又皆可为信笔。而三家文字皆如此。)
仁祖朝。(壬午)丁公子彦璜上疏讼其冤事。 下吏曹。吏曹回 启曰。 反正初。大论立异之人。(废 母后议)无论存没。皆蒙 褒典。独丁好宽以有前日负犯。(永昌出置之论)尚在罪籍。而功罪足相当。其子诉冤。又出至情。当有变通。而事系 恩典。 上裁何如。 启。 依允。(窃观此录。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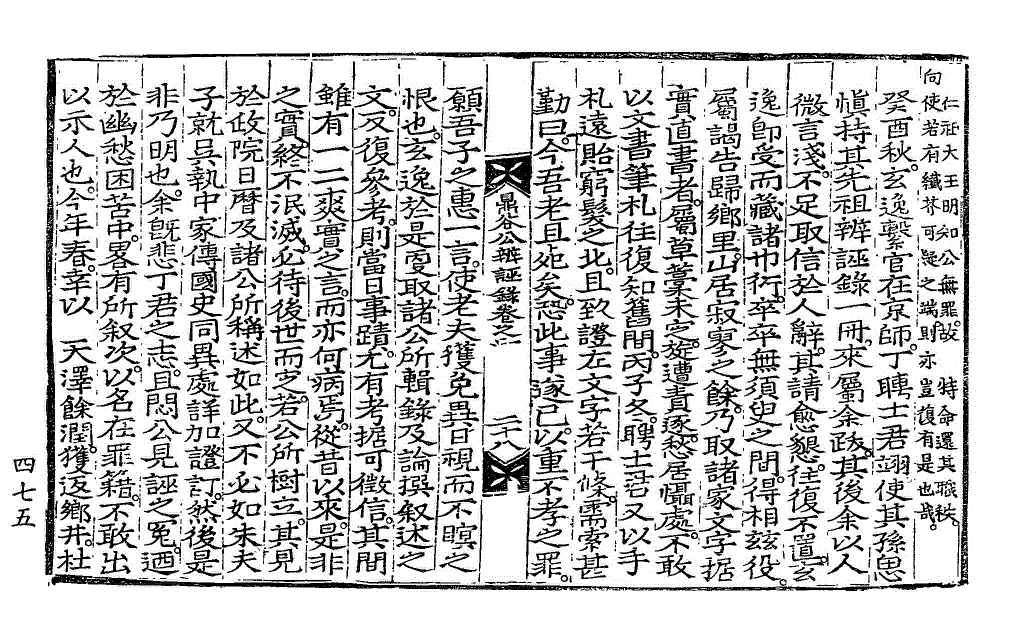 仁祖大王明知公无罪。故 特命还其职秩。向使若有纤芥可疑之端。则亦岂复有是也哉。)
仁祖大王明知公无罪。故 特命还其职秩。向使若有纤芥可疑之端。则亦岂复有是也哉。)癸酉秋。玄逸系官在京师。丁聘士君翊。使其孙思慎持其先祖辨诬录一册。来属余跋。其后余以人微言浅。不足取信于人辞。其请愈恳。往复不置。玄逸即受而藏诸巾衍。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相玆役。属谒告归乡里。山居寂寥之馀。乃取诸家文字据实直书者。属草稿未定。旋遭责逐。愁居慑处。不敢以文书笔札往复知旧间。丙子冬。聘士君又以手札远贻穷发之北。且致證左文字若干条。需索甚勤曰。今吾老且死矣。恐此事遂已。以重不孝之罪。愿吾子之惠一言。使老夫获免异日视而不瞑之恨也。玄逸于是更取诸公所辑录及论撰叙述之文。反复参考。则当日事迹。尤有考据可徵信。其间虽有一二爽实之言。而亦何病焉。从昔以来。是非之实终不泯灭。必待后世而定。若公所树立。其见于政院日历及诸公所称述如此。又不必如朱夫子就吴执中家传国史同异处详加證订。然后是非乃明也。余既悲丁君之志。且闷公见诬之冤。乃于幽愁困苦中。略有所叙次。以名在罪籍。不敢出以示人也。今年春。幸以 天泽馀润。获返乡井。杜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6H 页
 门穷巷。翻阅旧编。为之掩卷太息。既而丁君又以书来。更申前请。乃以其所尝编次者。书于辨诬录之下以归之。
门穷巷。翻阅旧编。为之掩卷太息。既而丁君又以书来。更申前请。乃以其所尝编次者。书于辨诬录之下以归之。上之二十六年上章执徐冬十二月己卯。载宁李玄逸书。
丁先生家藏汉阴碑文辨误诸说后语
呜呼。昏朝废 母后之变。尚忍言哉。明明我 朝。五伦中天如日月二三百年。忽然阴曀惨惔而沦丧之。是以造,讱之遗臭尚播于舆儓之口。虽三尺童子闻其名。固将掩耳而却走。而况士大夫自白于当时。而受汶汶于后世者乎。故持平丁公好宽。吾曾王父之内弟也。公之家世以厚德清名闻。而吾之幼也。人或有诮公以造,讱之事者。吾闻而窃骇之。然于当时事。未有所考。则无以置辨于其间。而亦不能无疑于心也。既长。闻今进善先生之风而往从之。先生即持平公孙也。乃获闻其先祖风范志槩之一二。固皆名流伟人之为者。而及见抗辞乎大论。伸枉于明时者。皆较然言有徵而事有据。如指诸掌。可考而信。决非子孙为亲讳者之为。然后有以知由与求也之必不为弑逆大故。而向之所骇然而疑者。于是焉始定。以为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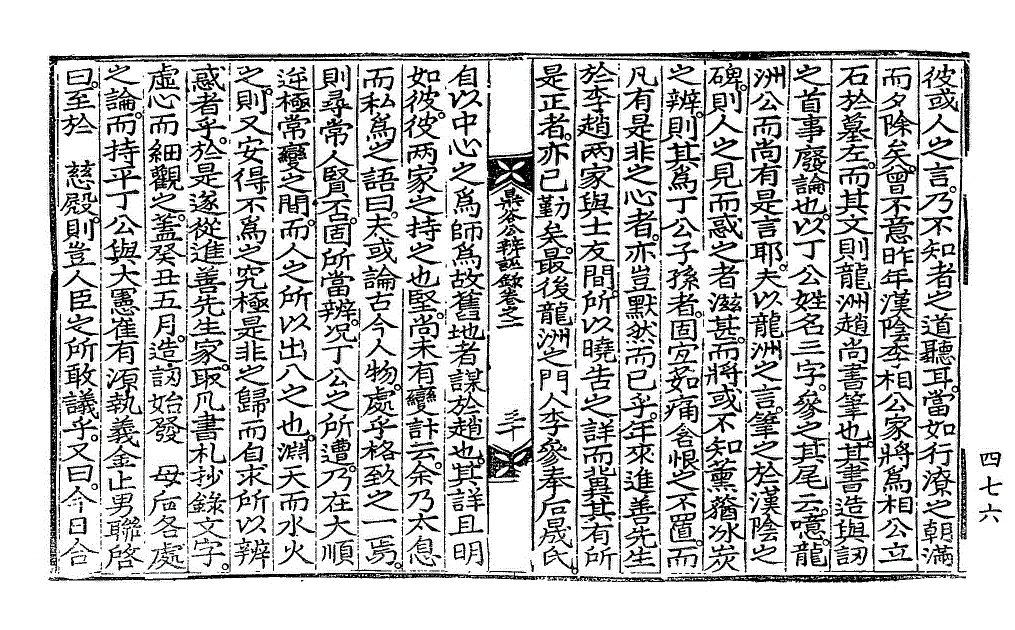 彼或人之言。乃不知者之道听耳。当如行潦之朝满而夕除矣。曾不意昨年汉阴李相公家将为相公立石于墓左。而其文则龙洲赵尚书笔也。其书造与讱之首事废论也。以丁公姓名三字。参之其尾云。噫。龙洲公而尚有是言耶。夫以龙洲之言。笔之于汉阴之碑。则人之见而惑之者滋甚。而将或不知薰莸冰炭之辨。则其为丁公子孙者。固宜茹痛含恨之不置。而凡有是非之心者。亦岂默然而已乎。年来进善先生于李,赵两家与士友间。所以晓告之详而冀其有所是正者。亦已勤矣。最后龙洲之门人李参奉后晟氏。自以中心之为师为故旧地者谋于赵也。其详且明如彼。彼两家之持之也坚。尚未有变计云。余乃太息而私为之语曰。夫或论古今人物。处乎格致之一焉。则寻常人贤否。固所当辨。况丁公之所遭。乃在大顺逆极常变之间。而人之所以出入之也。渊天而水火之。则又安得不为之究极是非之归而自求所以辨惑者乎。于是遂从进善先生家。取凡书札抄录文字。虚心而细观之。盖癸丑五月。造,讱始发 母后各处之论。而持平丁公与大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联启曰。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之所敢议乎。又曰。今日合
彼或人之言。乃不知者之道听耳。当如行潦之朝满而夕除矣。曾不意昨年汉阴李相公家将为相公立石于墓左。而其文则龙洲赵尚书笔也。其书造与讱之首事废论也。以丁公姓名三字。参之其尾云。噫。龙洲公而尚有是言耶。夫以龙洲之言。笔之于汉阴之碑。则人之见而惑之者滋甚。而将或不知薰莸冰炭之辨。则其为丁公子孙者。固宜茹痛含恨之不置。而凡有是非之心者。亦岂默然而已乎。年来进善先生于李,赵两家与士友间。所以晓告之详而冀其有所是正者。亦已勤矣。最后龙洲之门人李参奉后晟氏。自以中心之为师为故旧地者谋于赵也。其详且明如彼。彼两家之持之也坚。尚未有变计云。余乃太息而私为之语曰。夫或论古今人物。处乎格致之一焉。则寻常人贤否。固所当辨。况丁公之所遭。乃在大顺逆极常变之间。而人之所以出入之也。渊天而水火之。则又安得不为之究极是非之归而自求所以辨惑者乎。于是遂从进善先生家。取凡书札抄录文字。虚心而细观之。盖癸丑五月。造,讱始发 母后各处之论。而持平丁公与大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联启曰。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之所敢议乎。又曰。今日合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7H 页
 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云云。玉堂处置。仍斥造,讱而请出三臣者。其言具载当时政院日记誊本。凿凿可考。而金延兴悌男,姜贰相绅及梧里李相国诸家所录。不约而拜为之左契焉。夫然故丁公既乃摈于时。迁于海曲。而其后台启及儒疏。只斥造,讱,伟卿之为首恶。而无以丁公为言者。及白沙,苍石,愚伏之为汉阴为志为状。只书造,讱两贼。而丁公之名亦无所槩见。至于苍石之题丁观察之墓也。特书曰。公之兄某持不可云。其于立节之实状。可谓参伍辨證。而无毫发之可疑矣。是以当癸亥 改玉之初。虽因时流之觅疵。弃其立异之为节。独议其出置大君之罪而削其官。至壬午丁公之子监司公为掌令讼冤之日。该曹据事覆启而 仁庙许其伸雪焉。盖其丁公之所自立。夫既徵于时显于文献。达于 朝登闻于 君父者。其彰灼如彼。亦足以俟后来而无惑矣。又何龙洲之言之出而致此纷纷也。夫论人者质其心。论心者證其事。事證既实。心志既明。则天理在其中矣。于是举其在中之天理而论断其人。则人心服。而百世无异辞矣。今也龙洲之断丁公则不然。其于事證之实状。径庭如彼。岂其以当时
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云云。玉堂处置。仍斥造,讱而请出三臣者。其言具载当时政院日记誊本。凿凿可考。而金延兴悌男,姜贰相绅及梧里李相国诸家所录。不约而拜为之左契焉。夫然故丁公既乃摈于时。迁于海曲。而其后台启及儒疏。只斥造,讱,伟卿之为首恶。而无以丁公为言者。及白沙,苍石,愚伏之为汉阴为志为状。只书造,讱两贼。而丁公之名亦无所槩见。至于苍石之题丁观察之墓也。特书曰。公之兄某持不可云。其于立节之实状。可谓参伍辨證。而无毫发之可疑矣。是以当癸亥 改玉之初。虽因时流之觅疵。弃其立异之为节。独议其出置大君之罪而削其官。至壬午丁公之子监司公为掌令讼冤之日。该曹据事覆启而 仁庙许其伸雪焉。盖其丁公之所自立。夫既徵于时显于文献。达于 朝登闻于 君父者。其彰灼如彼。亦足以俟后来而无惑矣。又何龙洲之言之出而致此纷纷也。夫论人者质其心。论心者證其事。事證既实。心志既明。则天理在其中矣。于是举其在中之天理而论断其人。则人心服。而百世无异辞矣。今也龙洲之断丁公则不然。其于事證之实状。径庭如彼。岂其以当时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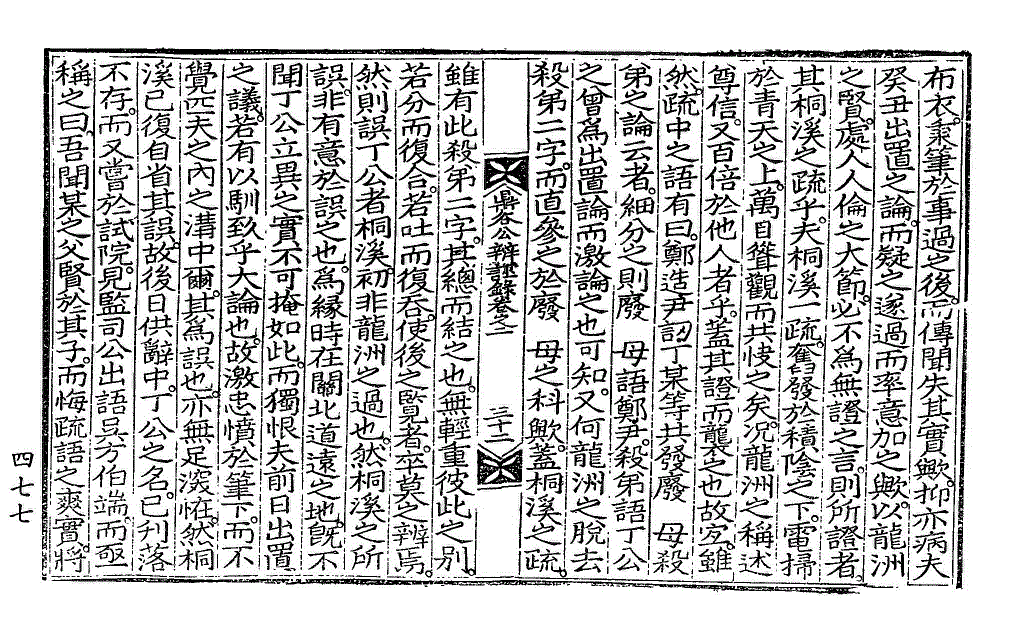 布衣。秉笔于事过之后。而传闻失其实欤。抑亦病夫癸丑出置之论。而疑之遂过而率意加之欤。以龙洲之贤。处人人伦之大节。必不为无證之言。则所證者。其桐溪之疏乎。夫桐溪一疏。奋发于积阴之下。电扫于青天之上。万目耸观而共快之矣。况龙洲之称述尊信。又百倍于他人者乎。盖其證而袭之也故宜。虽然。疏中之语有曰。郑造,尹讱,丁某等共发废 母杀弟之论云者。细分之则废 母语郑,尹。杀弟语丁公之曾为出置论而激论之也可知。又何龙洲之脱去杀弟二字。而直参之于废 母之科欤。盖桐溪之疏。虽有此杀弟二字。其总而结之也。无轻重彼此之别。若分而复合。若吐而复吞。使后之览者。卒莫之辨焉。然则误丁公者桐溪。初非龙洲之过也。然桐溪之所误。非有意于误之也。为缘时在关北道远之地。既不闻丁公立异之实不可掩如此。而独恨夫前日出置之议。若有以驯致乎大论也。故激忠愤于笔下。而不觉匹夫之内之沟中尔。其为误也。亦无足深怪。然桐溪已复自省其误。故后日供辞中。丁公之名。已刊落不存。而又尝于试院。见监司公出语吴方伯端。而亟称之曰。吾闻某之父贤于其子。而悔疏语之爽实。将
布衣。秉笔于事过之后。而传闻失其实欤。抑亦病夫癸丑出置之论。而疑之遂过而率意加之欤。以龙洲之贤。处人人伦之大节。必不为无證之言。则所證者。其桐溪之疏乎。夫桐溪一疏。奋发于积阴之下。电扫于青天之上。万目耸观而共快之矣。况龙洲之称述尊信。又百倍于他人者乎。盖其證而袭之也故宜。虽然。疏中之语有曰。郑造,尹讱,丁某等共发废 母杀弟之论云者。细分之则废 母语郑,尹。杀弟语丁公之曾为出置论而激论之也可知。又何龙洲之脱去杀弟二字。而直参之于废 母之科欤。盖桐溪之疏。虽有此杀弟二字。其总而结之也。无轻重彼此之别。若分而复合。若吐而复吞。使后之览者。卒莫之辨焉。然则误丁公者桐溪。初非龙洲之过也。然桐溪之所误。非有意于误之也。为缘时在关北道远之地。既不闻丁公立异之实不可掩如此。而独恨夫前日出置之议。若有以驯致乎大论也。故激忠愤于笔下。而不觉匹夫之内之沟中尔。其为误也。亦无足深怪。然桐溪已复自省其误。故后日供辞中。丁公之名。已刊落不存。而又尝于试院。见监司公出语吴方伯端。而亟称之曰。吾闻某之父贤于其子。而悔疏语之爽实。将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8H 页
 以陈达于 筵中。旋以去豳之扰未果云。是则桐溪疏斥丁公之语。果何足證哉。但桐溪陈达之举。既未果焉。而心知其误之说。人未及尽闻。则宜乎龙洲之亦不得闻而卒守其误也。一误之后。随所接而长。故其撰桐溪碑文及他文字。亦如汉相碑文中所书。而且道丁某见桐溪疏。叹曰我不免为千古罪人。因纵饮至死云。此无他。先入者之常主乎中。而窃铁之疑。无所不至故也。昔以刘共父,张南轩之贤。尚不免于以一个胡文定横在肚里。更不顾义理之讥。又何疑于龙洲之主桐溪而不暇他考乎。至于丁公自责之说。吾尝闻之于进善先生。其言曰。先祖气貌俊伟。局量宽厚。一时名流皆推许焉。及其为大君出置之论也。实出于远嫌猜图全安之厚意。而当时名公硕人亦有以肯可乎此者。顾于几微之际。有所不审。阶乱者得以藉乎其口而导迎。其下流遂至滔天之域。故以公本心之厚。其自反也。亦过于厚。未尝自多其立异之为大。而深自悲愤乎东隅之既失。向人言语。辄发悔恨之辞。时复引侣含杯。以消遣平生之怀。是以人之观之者。或得于外而不得于其内。不能以知人之智观公。以公责己之深證公以断之。此公之素心。
以陈达于 筵中。旋以去豳之扰未果云。是则桐溪疏斥丁公之语。果何足證哉。但桐溪陈达之举。既未果焉。而心知其误之说。人未及尽闻。则宜乎龙洲之亦不得闻而卒守其误也。一误之后。随所接而长。故其撰桐溪碑文及他文字。亦如汉相碑文中所书。而且道丁某见桐溪疏。叹曰我不免为千古罪人。因纵饮至死云。此无他。先入者之常主乎中。而窃铁之疑。无所不至故也。昔以刘共父,张南轩之贤。尚不免于以一个胡文定横在肚里。更不顾义理之讥。又何疑于龙洲之主桐溪而不暇他考乎。至于丁公自责之说。吾尝闻之于进善先生。其言曰。先祖气貌俊伟。局量宽厚。一时名流皆推许焉。及其为大君出置之论也。实出于远嫌猜图全安之厚意。而当时名公硕人亦有以肯可乎此者。顾于几微之际。有所不审。阶乱者得以藉乎其口而导迎。其下流遂至滔天之域。故以公本心之厚。其自反也。亦过于厚。未尝自多其立异之为大。而深自悲愤乎东隅之既失。向人言语。辄发悔恨之辞。时复引侣含杯。以消遣平生之怀。是以人之观之者。或得于外而不得于其内。不能以知人之智观公。以公责己之深證公以断之。此公之素心。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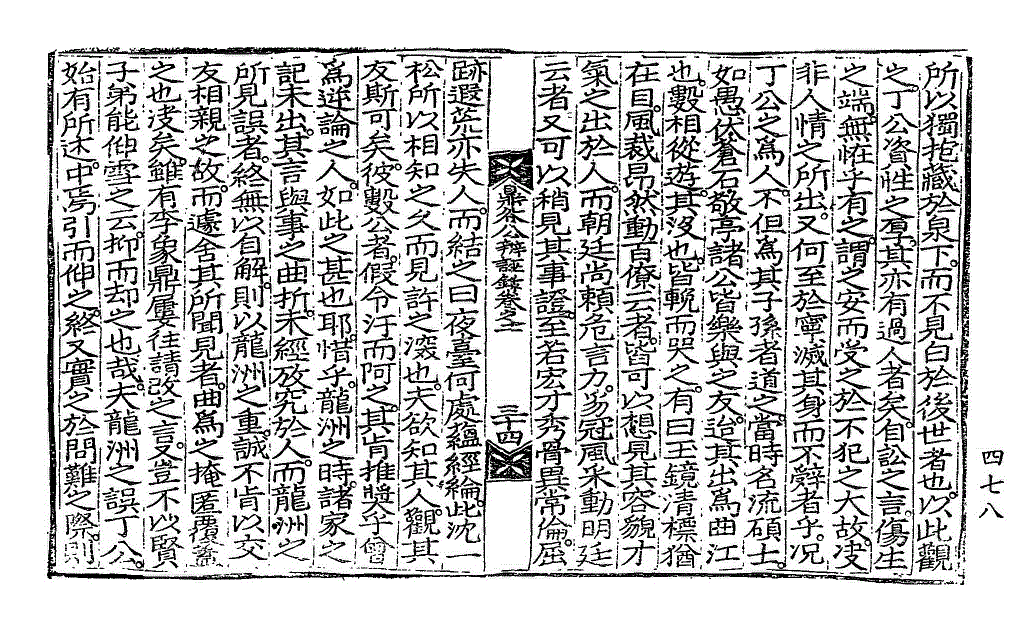 所以独抱藏于泉下。而不见白于后世者也。以此观之。丁公资性之厚。其亦有过人者矣。自讼之言。伤生之端。无怪乎有之。谓之安而受之于不犯之大故。决非人情之所出。又何至于宁灭其身而不辞者乎。况丁公之为人。不但为其子孙者道之。当时名流硕士。如愚伏,苍石,敬亭诸公皆乐与之友。迨其出为曲江也。数相从游。其没也。皆挽而哭之。有曰玉镜清标犹在目。风裁昂然动百僚云者。皆可以想见其容貌才气之出于人。而朝廷尚赖危言力。貌冠风采动明廷云者。又可以稍见其事證。至若宏才秀骨异常伦。屈迹遐荒亦失人。而结之曰夜台何处蕴经纶。此沈一松所以相知之久而见许之深也。夫欲知其人。观其友斯可矣。彼数公者。假令污而阿之。其肯推奖乎会为逆论之人。如此之甚也耶。惜乎。龙洲之时。诸家之记未出。其言与事之曲折。未经考究于人。而龙洲之所见误者。终无以自解。则以龙洲之重。诚不肯以交友相亲之故。而遽舍其所闻见者。曲为之掩匿覆盖之也决矣。虽有李象鼎屡往请改之言。又岂不以贤子弟能伸雪之云。抑而却之也哉。夫龙洲之误丁公。始有所述。中焉引而伸之。终又实之于问难之际。则
所以独抱藏于泉下。而不见白于后世者也。以此观之。丁公资性之厚。其亦有过人者矣。自讼之言。伤生之端。无怪乎有之。谓之安而受之于不犯之大故。决非人情之所出。又何至于宁灭其身而不辞者乎。况丁公之为人。不但为其子孙者道之。当时名流硕士。如愚伏,苍石,敬亭诸公皆乐与之友。迨其出为曲江也。数相从游。其没也。皆挽而哭之。有曰玉镜清标犹在目。风裁昂然动百僚云者。皆可以想见其容貌才气之出于人。而朝廷尚赖危言力。貌冠风采动明廷云者。又可以稍见其事證。至若宏才秀骨异常伦。屈迹遐荒亦失人。而结之曰夜台何处蕴经纶。此沈一松所以相知之久而见许之深也。夫欲知其人。观其友斯可矣。彼数公者。假令污而阿之。其肯推奖乎会为逆论之人。如此之甚也耶。惜乎。龙洲之时。诸家之记未出。其言与事之曲折。未经考究于人。而龙洲之所见误者。终无以自解。则以龙洲之重。诚不肯以交友相亲之故。而遽舍其所闻见者。曲为之掩匿覆盖之也决矣。虽有李象鼎屡往请改之言。又岂不以贤子弟能伸雪之云。抑而却之也哉。夫龙洲之误丁公。始有所述。中焉引而伸之。终又实之于问难之际。则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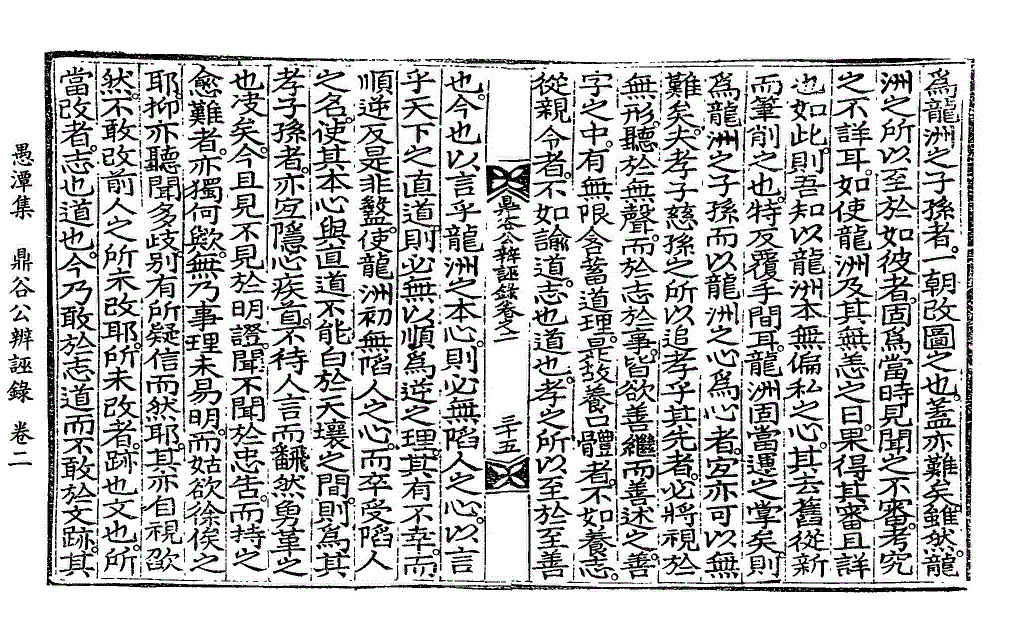 为龙洲之子孙者。一朝改图之也。盖亦难矣。虽然。龙洲之所以至于如彼者。固为当时见闻之不审。考究之不详耳。如使龙洲及其无恙之日。果得其审且详也如此。则吾知以龙洲本无偏私之心。其去旧从新而笔削之也。特反覆手间耳。龙洲固当运之掌矣。则为龙洲之子孙而以龙洲之心为心者。宜亦可以无难矣。夫孝子慈孙之所以追孝乎其先者。必将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而于志于事。皆欲善继而善述之。善字之中。有无限含蓄道理。是故养口体者。不如养志。从亲令者。不如谕道。志也道也。孝之所以至于至善也。今也以言乎龙洲之本心。则必无陷人之心。以言乎天下之直道。则必无以顺为逆之理。其有不幸。而顺逆反是非盭。使龙洲初无陷人之心。而卒受陷人之名。使其本心与直道不能白于天壤之间。则为其孝子孙者。亦宜隐心疾首。不待人言而翻然勇革之也决矣。今且见不见于明證。闻不闻于忠告。而持之愈难者。亦独何欤。无乃事理未易明。而姑欲徐俟之耶。抑亦听闻多岐。别有所疑信而然耶。其亦自视欿然。不敢改前人之所未改耶。所未改者。迹也文也。所当改者。志也道也。今乃敢于志道而不敢于文迹。其
为龙洲之子孙者。一朝改图之也。盖亦难矣。虽然。龙洲之所以至于如彼者。固为当时见闻之不审。考究之不详耳。如使龙洲及其无恙之日。果得其审且详也如此。则吾知以龙洲本无偏私之心。其去旧从新而笔削之也。特反覆手间耳。龙洲固当运之掌矣。则为龙洲之子孙而以龙洲之心为心者。宜亦可以无难矣。夫孝子慈孙之所以追孝乎其先者。必将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而于志于事。皆欲善继而善述之。善字之中。有无限含蓄道理。是故养口体者。不如养志。从亲令者。不如谕道。志也道也。孝之所以至于至善也。今也以言乎龙洲之本心。则必无陷人之心。以言乎天下之直道。则必无以顺为逆之理。其有不幸。而顺逆反是非盭。使龙洲初无陷人之心。而卒受陷人之名。使其本心与直道不能白于天壤之间。则为其孝子孙者。亦宜隐心疾首。不待人言而翻然勇革之也决矣。今且见不见于明證。闻不闻于忠告。而持之愈难者。亦独何欤。无乃事理未易明。而姑欲徐俟之耶。抑亦听闻多岐。别有所疑信而然耶。其亦自视欿然。不敢改前人之所未改耶。所未改者。迹也文也。所当改者。志也道也。今乃敢于志道而不敢于文迹。其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79L 页
 将谓志道轻而文迹重乎。其或疑之。何不明言而反复之。如或俟之。又谁将终而刻之。是未可晓也已。龙洲家以文字主人。既不肯删误。故汉阴诸孙亦不能有所改正。于是将以移玷于先公不朽之碑而不暇恤。两家子孙之所见。其不相上下也如是。可慨也已。今闻进善先生家既不见两家之往复裁度以适乎事理之宜。故亦将收录文迹。传之方来。将以讼于后世之子云。而明其先祖之为人所诬者云。李参奉所谓苦事苦事者。诚在于是。则其为两家者。亦岂独晏然而已哉。如曰不然而守株乎桐溪,龙洲宿昔之误。卒莫之变焉。则其将曰诸家誊本立异文字。尽皆赝作欤。白沙之志文。言者之疏章。尽皆漏网欤。苍石诸公其将护逆欤。丁公之见黜于昏朝。谓之媚世行宠欤。癸亥被驳。不以大论。其失勘断欤。壬午伸冤而赠爵。其将以褒恶欤。抑亦论人之心者。不当證其事欤。其断无是理也必矣。最可笑者。或者之说曰。丁公既参于出置之论。故后虽有立异之举。亦欲以掩前过耳。其心则犹未革也。故龙洲之笔。特诛其心耳。噫。是何言也。圣贤之于人。不念其旧而与其自新。夷而不夷则进之。恶而变恶则予之。如春秋纲目之文。班班
将谓志道轻而文迹重乎。其或疑之。何不明言而反复之。如或俟之。又谁将终而刻之。是未可晓也已。龙洲家以文字主人。既不肯删误。故汉阴诸孙亦不能有所改正。于是将以移玷于先公不朽之碑而不暇恤。两家子孙之所见。其不相上下也如是。可慨也已。今闻进善先生家既不见两家之往复裁度以适乎事理之宜。故亦将收录文迹。传之方来。将以讼于后世之子云。而明其先祖之为人所诬者云。李参奉所谓苦事苦事者。诚在于是。则其为两家者。亦岂独晏然而已哉。如曰不然而守株乎桐溪,龙洲宿昔之误。卒莫之变焉。则其将曰诸家誊本立异文字。尽皆赝作欤。白沙之志文。言者之疏章。尽皆漏网欤。苍石诸公其将护逆欤。丁公之见黜于昏朝。谓之媚世行宠欤。癸亥被驳。不以大论。其失勘断欤。壬午伸冤而赠爵。其将以褒恶欤。抑亦论人之心者。不当證其事欤。其断无是理也必矣。最可笑者。或者之说曰。丁公既参于出置之论。故后虽有立异之举。亦欲以掩前过耳。其心则犹未革也。故龙洲之笔。特诛其心耳。噫。是何言也。圣贤之于人。不念其旧而与其自新。夷而不夷则进之。恶而变恶则予之。如春秋纲目之文。班班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80H 页
 然可考矣。今丁公之小失在前。其竖大节也在后。龙洲公独诛其心而不与之为善。则是龙洲讨恶之严。将有贤于尼父,晦翁者乎。且百僚廷请正律永昌之日。汉阴,白沙以下莫不皆参。则龙洲之笔。其将人人而诛之乎。是则龙洲之予夺不均。亿逆太过。邈无乐成美之盛意尔。岂不亦诬龙洲之甚乎。但此一事。作戒数段则有之。当永昌之出置也。丁公先发其论。而竟以藉乎奸贼之手。骎骎乎履霜坚冰之惨。以至终身悔恨而不可复。其见几之不明。为戒一也。桐溪。龙洲之斥丁公。听闻未精。考据不博。言之太快。持之太固。遂起后人之争端。其论人之不审。为戒二也。且夫两公之贤。为众人之所宗信。故人见其误而不以为误。其为误也愈甚。其责备贤者之义。为戒三也。李,赵两家胶于旧闻。忽于新得。不能体先志据直道。衡铨而绳削之。俾有光于前烈。此其见事之迟处心之固。为戒四也。此则凡为格物致知之学者。盖不可不知也。虽然。义理无穷。见闻有限。而公天下之是非。非一二人之私议。安知自今以往。事之旁通者愈博。言之后出者愈明。而人人之闻之者。亦将如我之既骇而疑。既疑而始知者。而卒为百世之定论者乎。此实丁
然可考矣。今丁公之小失在前。其竖大节也在后。龙洲公独诛其心而不与之为善。则是龙洲讨恶之严。将有贤于尼父,晦翁者乎。且百僚廷请正律永昌之日。汉阴,白沙以下莫不皆参。则龙洲之笔。其将人人而诛之乎。是则龙洲之予夺不均。亿逆太过。邈无乐成美之盛意尔。岂不亦诬龙洲之甚乎。但此一事。作戒数段则有之。当永昌之出置也。丁公先发其论。而竟以藉乎奸贼之手。骎骎乎履霜坚冰之惨。以至终身悔恨而不可复。其见几之不明。为戒一也。桐溪。龙洲之斥丁公。听闻未精。考据不博。言之太快。持之太固。遂起后人之争端。其论人之不审。为戒二也。且夫两公之贤。为众人之所宗信。故人见其误而不以为误。其为误也愈甚。其责备贤者之义。为戒三也。李,赵两家胶于旧闻。忽于新得。不能体先志据直道。衡铨而绳削之。俾有光于前烈。此其见事之迟处心之固。为戒四也。此则凡为格物致知之学者。盖不可不知也。虽然。义理无穷。见闻有限。而公天下之是非。非一二人之私议。安知自今以往。事之旁通者愈博。言之后出者愈明。而人人之闻之者。亦将如我之既骇而疑。既疑而始知者。而卒为百世之定论者乎。此实丁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二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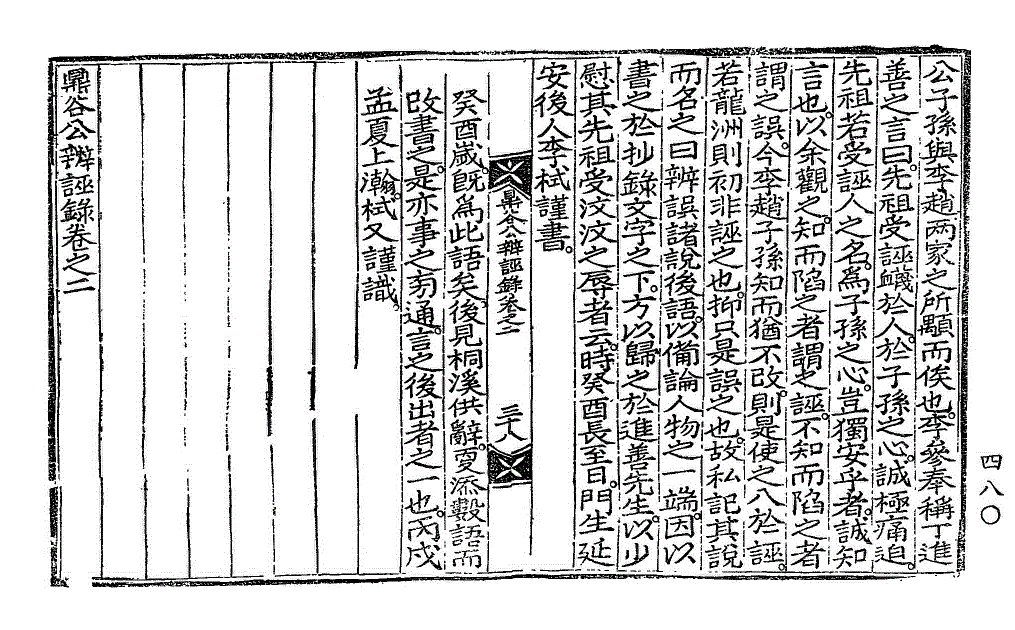 公子孙与李,赵两家之所颙而俟也。李参奉称丁进善之言曰。先祖受诬蔑于人。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若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者。诚知言也。以余观之。知而陷之者谓之诬。不知而陷之者谓之误。今李赵子孙知而犹不改。则是使之入于诬。若龙洲则初非诬之也。抑只是误之也。故私记其说而名之曰辨误诸说后语。以备论人物之一端。因以书之于抄录文字之下。方以归之于进善先生。以少慰其先祖受汶汶之辱者云。时癸酉长至日。门生延安后人李栻谨书。
公子孙与李,赵两家之所颙而俟也。李参奉称丁进善之言曰。先祖受诬蔑于人。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若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者。诚知言也。以余观之。知而陷之者谓之诬。不知而陷之者谓之误。今李赵子孙知而犹不改。则是使之入于诬。若龙洲则初非诬之也。抑只是误之也。故私记其说而名之曰辨误诸说后语。以备论人物之一端。因以书之于抄录文字之下。方以归之于进善先生。以少慰其先祖受汶汶之辱者云。时癸酉长至日。门生延安后人李栻谨书。[识(李栻)]
癸酉岁。既为此语矣。后见桐溪供辞。更添数语而改书之。是亦事之旁通。言之后出者之一也。丙戌孟夏上瀚。栻又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