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x 页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杂著
杂著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1H 页
 太极图说。示舍弟季文兼示玄石。(己未正月)
太极图说。示舍弟季文兼示玄石。(己未正月)太极图说解曰。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夫太极。理也。性亦理也。非二物也。人物之性。不能无偏全则何以曰全体各具耶。乞赐明教。(右季文问玄石书)
示谕谨悉。所谓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云者。只是欲明五行各具之性。其本皆从太极之全体出来。初无不同焉耳。其实太极之全体。决无该遍合同于各具之中之理。何者。原天命流行之始。固无人物偏全之异。而逮形气拘滞之后。又因物之刚柔大小而自致其理之不同。所以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火之性。非复原初浑然太极之全体然也。盖此文义。正如中庸章句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者。然其实健顺五常之德。有非万物之所得尽。则是亦从其本而言之故也。今于此等处。不能沈潜反复。活看而默识之。涣然自得于圣贤言意之外。而必欲强求太极全体于五行各具之中。所谓以辞害意。殆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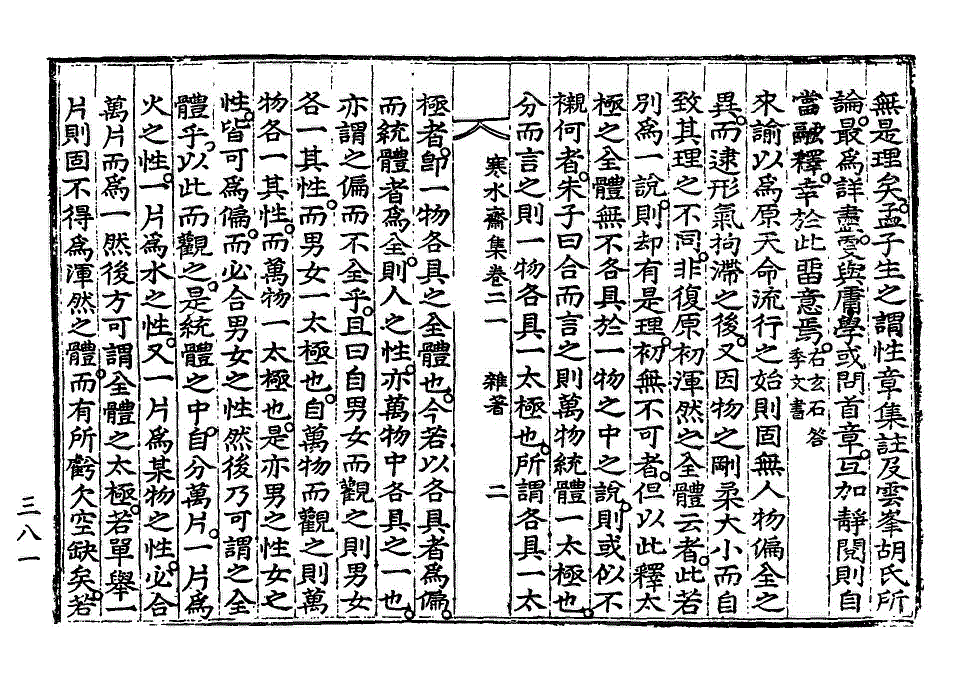 无是理矣。孟子生之谓性章集注及云峰胡氏所论。最为详尽。更与庸,学或问首章。互加静阅则自当融释。幸于此留意焉。(右玄石答季文书)
无是理矣。孟子生之谓性章集注及云峰胡氏所论。最为详尽。更与庸,学或问首章。互加静阅则自当融释。幸于此留意焉。(右玄石答季文书)来谕以为原天命流行之始则固无人物偏全之异。而逮形气拘滞之后。又因物之刚柔大小而自致其理之不同。非复原初浑然之全体云者。此若别为一说。则却有是理。初无不可者。但以此释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之说。则或似不衬何者。朱子曰合而言之则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则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各具一太极者。即一物各具之全体也。今若以各具者为偏。而统体者为全。则人之性。亦万物中各具之一也。亦谓之偏而不全乎。且曰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是亦男之性女之性。皆可为偏。而必合男女之性然后乃可谓之全体乎。以此而观之。是统体之中。自分万片。一片为火之性。一片为水之性。又一片为某物之性。必合万片而为一然后方可谓全体之太极。若单举一片则固不得为浑然之体。而有所亏欠空缺矣。若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2H 页
 如是。则万物所禀之性。只当曰太极之一端。而不当曰一太极。只当曰偏。而不当曰全体。只当曰各得。而不当曰各具也。来谕又谓所谓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云者。只是欲明五行之性其本皆从太极之全体中出来。而其实太极之全体决无该遍合同于各具之中之理。若此段本意果如此。而其中语势乃如彼。则不但理有所局。文势亦似不顺。此老平生言语明白易晓。决不若是之未莹也。此实可疑也。幸乞更赐详教。(右季文再问玄石书)
如是。则万物所禀之性。只当曰太极之一端。而不当曰一太极。只当曰偏。而不当曰全体。只当曰各得。而不当曰各具也。来谕又谓所谓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云者。只是欲明五行之性其本皆从太极之全体中出来。而其实太极之全体决无该遍合同于各具之中之理。若此段本意果如此。而其中语势乃如彼。则不但理有所局。文势亦似不顺。此老平生言语明白易晓。决不若是之未莹也。此实可疑也。幸乞更赐详教。(右季文再问玄石书)前日太极全体之说。每为左右思之。未得其衷。适与金君士直邂逅。言及此事。似亦无所参差。遂更商量。始知鄙人所以仰报者。诚有未尽。盖其所谓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火之性。非复原初浑然太极之全体者。固自正当。第其所以为水火者。无论精粗大小。莫不自然完具于其中。是亦可谓浑然太极之全体而无所妨者。此本图解之意。而不能深会。至谓是亦从其本而言之。则其误大矣。常考其总论。有曰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2L 页
 又通书理性命章小注。问如此则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犬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分也。又曰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个个完全。又将百粒去种。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以此推之。水中之月。非真天上之月。而为月则同。百粒之粟。非真一粒之粟。而为粟则同。此乃可谓浑然太极之全体而无所妨者。然其所谓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火之性。非复原初浑然太极之全体。则终有在也。如是说得。上下周遍。方无透漏。未知于雅旨复以为如何耳。(右玄石再答季文书)
又通书理性命章小注。问如此则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犬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分也。又曰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个个完全。又将百粒去种。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以此推之。水中之月。非真天上之月。而为月则同。百粒之粟。非真一粒之粟。而为粟则同。此乃可谓浑然太极之全体而无所妨者。然其所谓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火之性。非复原初浑然太极之全体。则终有在也。如是说得。上下周遍。方无透漏。未知于雅旨复以为如何耳。(右玄石再答季文书)语其理则无不全。论其性则有偏全。何者。天赋之理则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先儒曰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看则不分晓。不合看。又离了不相干涉。知斯说则几矣。盖尝论之。盈天地之间者。莫非物也。而物物之中。莫不有所以然之理。斯理也。命之曰太极。太极者。极至之谓也。何以谓之极至也。其为体。至神至妙。不可名状。故特强名之耳。是以论其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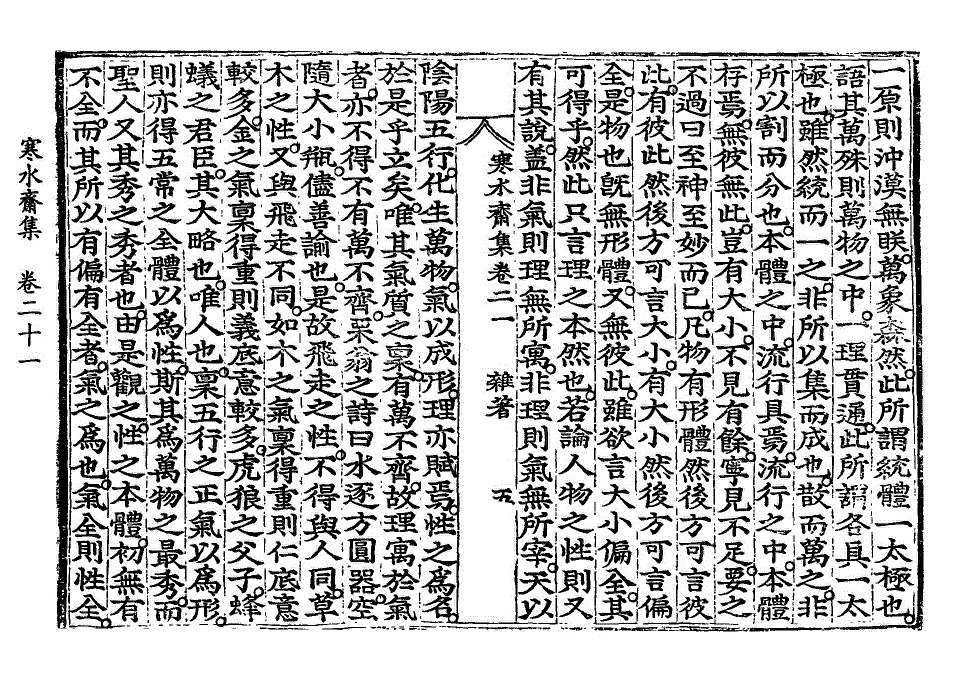 一原则冲漠无眹。万象森然。此所谓统体一太极也。语其万殊则万物之中。一理贯通。此所谓各具一太极也。虽然统而一之。非所以集而成也。散而万之。非所以割而分也。本体之中。流行具焉。流行之中。本体存焉。无彼无此。岂有大小。不见有馀。宁见不足。要之不过曰至神至妙而已。凡物有形体然后方可言彼此。有彼此然后方可言大小。有大小然后方可言偏全。是物也既无形体。又无彼此。虽欲言大小偏全。其可得乎。然此只言理之本然也。若论人物之性则又有其说。盖非气则理无所寓。非理则气无所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性之为名。于是乎立矣。唯其气质之禀。有万不齐。故理寓于气者。亦不得不有万不齐。栗翁之诗曰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尽善谕也。是故飞走之性。不得与人同。草木之性。又与飞走不同。如木之气禀得重则仁底意较多。金之气禀得重则义底意较多。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其大略也。唯人也。禀五行之正气以为形。则亦得五常之全体以为性。斯其为万物之最秀。而圣人又其秀之秀者也。由是观之。性之本体。初无有不全。而其所以有偏有全者。气之为也。气全则性全。
一原则冲漠无眹。万象森然。此所谓统体一太极也。语其万殊则万物之中。一理贯通。此所谓各具一太极也。虽然统而一之。非所以集而成也。散而万之。非所以割而分也。本体之中。流行具焉。流行之中。本体存焉。无彼无此。岂有大小。不见有馀。宁见不足。要之不过曰至神至妙而已。凡物有形体然后方可言彼此。有彼此然后方可言大小。有大小然后方可言偏全。是物也既无形体。又无彼此。虽欲言大小偏全。其可得乎。然此只言理之本然也。若论人物之性则又有其说。盖非气则理无所寓。非理则气无所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性之为名。于是乎立矣。唯其气质之禀。有万不齐。故理寓于气者。亦不得不有万不齐。栗翁之诗曰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尽善谕也。是故飞走之性。不得与人同。草木之性。又与飞走不同。如木之气禀得重则仁底意较多。金之气禀得重则义底意较多。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其大略也。唯人也。禀五行之正气以为形。则亦得五常之全体以为性。斯其为万物之最秀。而圣人又其秀之秀者也。由是观之。性之本体。初无有不全。而其所以有偏有全者。气之为也。气全则性全。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3L 页
 气偏则性偏。又何疑乎。是以栗翁之言曰。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气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惟此一言。可谓发千古不传之妙矣。嗟乎。非知道者。谁能识之。客有难之者曰。性即理也。理即性也。今子析而二之。无乃太剧分开乎。曰此非某之所刱也。圣贤已言之。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朱先生曰仁义礼智。犹是成之者性。上面又有一阴一阳之道。继之者善。先生又印或人之问。谓之理同则可。谓之性同则不可。经传所载。此类甚多。子归而考之可也。
气偏则性偏。又何疑乎。是以栗翁之言曰。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气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惟此一言。可谓发千古不传之妙矣。嗟乎。非知道者。谁能识之。客有难之者曰。性即理也。理即性也。今子析而二之。无乃太剧分开乎。曰此非某之所刱也。圣贤已言之。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朱先生曰仁义礼智。犹是成之者性。上面又有一阴一阳之道。继之者善。先生又印或人之问。谓之理同则可。谓之性同则不可。经传所载。此类甚多。子归而考之可也。论性说(戊戌)
圣贤论性。其说大槩有三。有除却气。单指理而言之者。有各指其气之理。而亦不杂乎其气而为言者。有以理与气杂而言者。专指理而言则太极全体。无物不具。而万物之性皆同矣。是则一原也。而朱子所谓一物各具一太极者也。各指其气之理而言则阳健阴顺。木仁火礼金义水智。其性不同。而亦不杂乎其气之清浊美恶而言。故其为健顺五常。犹不失为至善。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而人物之性不同矣。是则分殊也。而朱子所谓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4H 页
 这是异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便是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者也。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则刚柔善恶。有万不齐。人人物物之性。皆不同矣。是则分殊之分殊也。朱子所谓刚柔善恶极多般样。千般百种。不可穷究者也。虽然太极全体。随其阴阳五行所寓之气而名。其为是气之性者。为健顺五常。健顺五常之性。杂其气质清浊美恶有万不齐者而言者。为气质之性。则其实只是一性也。今之学者。只知有单指理杂理气之说。而不知有各指其气之理而亦不杂乎其气之说。故其论健顺五常。同之于各具太极之义。谓阳亦具健顺五常。阴亦具健顺五常。草木禽兽。莫不各具健顺五常。而于经传所论健顺五常。人物不同禀之说。则一切皆归之于气质善恶之性。岂不可笑也。大率其病在于性道本原义理精微处。初不可以几及。而依俙闻得道理名目。髣髴窥见性情光影。便自拟以豁然大悟。轻肆自信。大言来辨。甚可闷叹。愚于未发论心。其说亦尝有三。曰未发之心。无善恶之可言。李器甫非之而拟之于胡氏之性无善恶。又曰未发前气质亦有清浊善恶之不齐。李公举非之而拟之于荀扬之性恶性混。又曰未发之心。何尝有
这是异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便是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者也。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则刚柔善恶。有万不齐。人人物物之性。皆不同矣。是则分殊之分殊也。朱子所谓刚柔善恶极多般样。千般百种。不可穷究者也。虽然太极全体。随其阴阳五行所寓之气而名。其为是气之性者。为健顺五常。健顺五常之性。杂其气质清浊美恶有万不齐者而言者。为气质之性。则其实只是一性也。今之学者。只知有单指理杂理气之说。而不知有各指其气之理而亦不杂乎其气之说。故其论健顺五常。同之于各具太极之义。谓阳亦具健顺五常。阴亦具健顺五常。草木禽兽。莫不各具健顺五常。而于经传所论健顺五常。人物不同禀之说。则一切皆归之于气质善恶之性。岂不可笑也。大率其病在于性道本原义理精微处。初不可以几及。而依俙闻得道理名目。髣髴窥见性情光影。便自拟以豁然大悟。轻肆自信。大言来辨。甚可闷叹。愚于未发论心。其说亦尝有三。曰未发之心。无善恶之可言。李器甫非之而拟之于胡氏之性无善恶。又曰未发前气质亦有清浊善恶之不齐。李公举非之而拟之于荀扬之性恶性混。又曰未发之心。何尝有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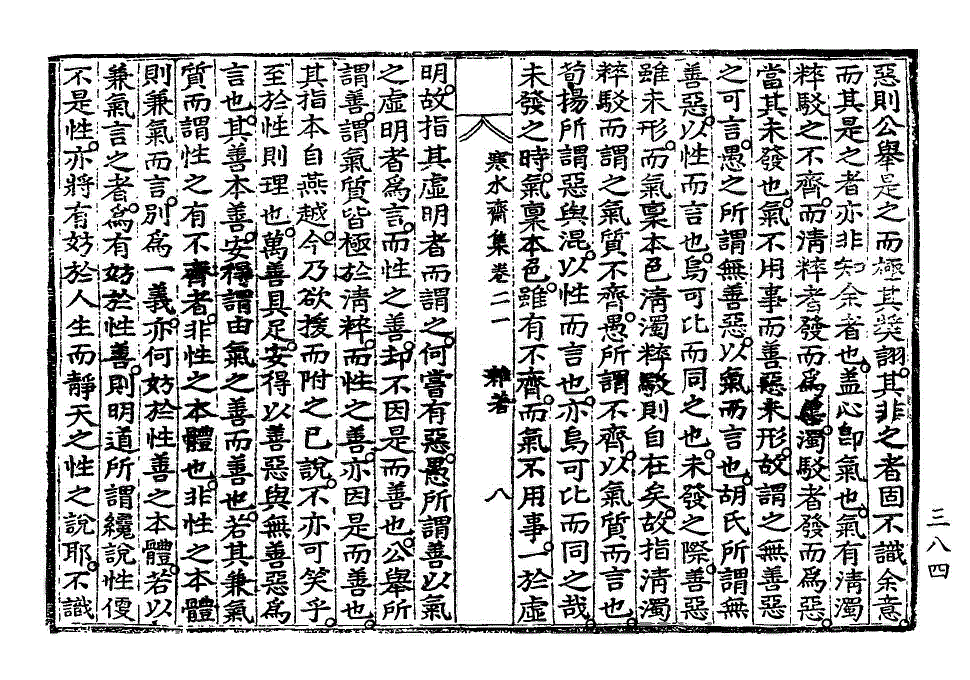 恶则公举是之而极其奖诩。其非之者固不识余意。而其是之者亦非知余者也。盖心即气也。气有清浊粹驳之不齐。而清粹者发而为善。浊驳者发而为恶。当其未发也。气不用事而善恶未形。故谓之无善恶之可言。愚之所谓无善恶。以气而言也。胡氏所谓无善恶。以性而言也。乌可比而同之也。未发之际。善恶虽未形。而气禀本色清浊粹驳则自在矣。故指清浊粹驳而谓之气质不齐。愚所谓不齐。以气质而言也。荀,扬所谓恶与混。以性而言也。亦乌可比而同之哉。未发之时。气禀本色。虽有不齐。而气不用事。一于虚明。故指其虚明者而谓之。何尝有恶。愚所谓善。以气之虚明者为言。而性之善。却不因是而善也。公举所谓善。谓气质皆极于清粹。而性之善。亦因是而善也。其指本自燕越。今乃欲援而附之己说。不亦可笑乎。至于性则理也。万善具足。安得以善恶与无善恶为言也。其善本善。安得谓由气之善而善也。若其兼气质而谓性之有不齐者。非性之本体也。非性之本体则兼气而言。别为一义。亦何妨于性善之本体。若以兼气言之者。为有妨于性善。则明道所谓才说性便不是性。亦将有妨于人生而静天之性之说耶。不识
恶则公举是之而极其奖诩。其非之者固不识余意。而其是之者亦非知余者也。盖心即气也。气有清浊粹驳之不齐。而清粹者发而为善。浊驳者发而为恶。当其未发也。气不用事而善恶未形。故谓之无善恶之可言。愚之所谓无善恶。以气而言也。胡氏所谓无善恶。以性而言也。乌可比而同之也。未发之际。善恶虽未形。而气禀本色清浊粹驳则自在矣。故指清浊粹驳而谓之气质不齐。愚所谓不齐。以气质而言也。荀,扬所谓恶与混。以性而言也。亦乌可比而同之哉。未发之时。气禀本色。虽有不齐。而气不用事。一于虚明。故指其虚明者而谓之。何尝有恶。愚所谓善。以气之虚明者为言。而性之善。却不因是而善也。公举所谓善。谓气质皆极于清粹。而性之善。亦因是而善也。其指本自燕越。今乃欲援而附之己说。不亦可笑乎。至于性则理也。万善具足。安得以善恶与无善恶为言也。其善本善。安得谓由气之善而善也。若其兼气质而谓性之有不齐者。非性之本体也。非性之本体则兼气而言。别为一义。亦何妨于性善之本体。若以兼气言之者。为有妨于性善。则明道所谓才说性便不是性。亦将有妨于人生而静天之性之说耶。不识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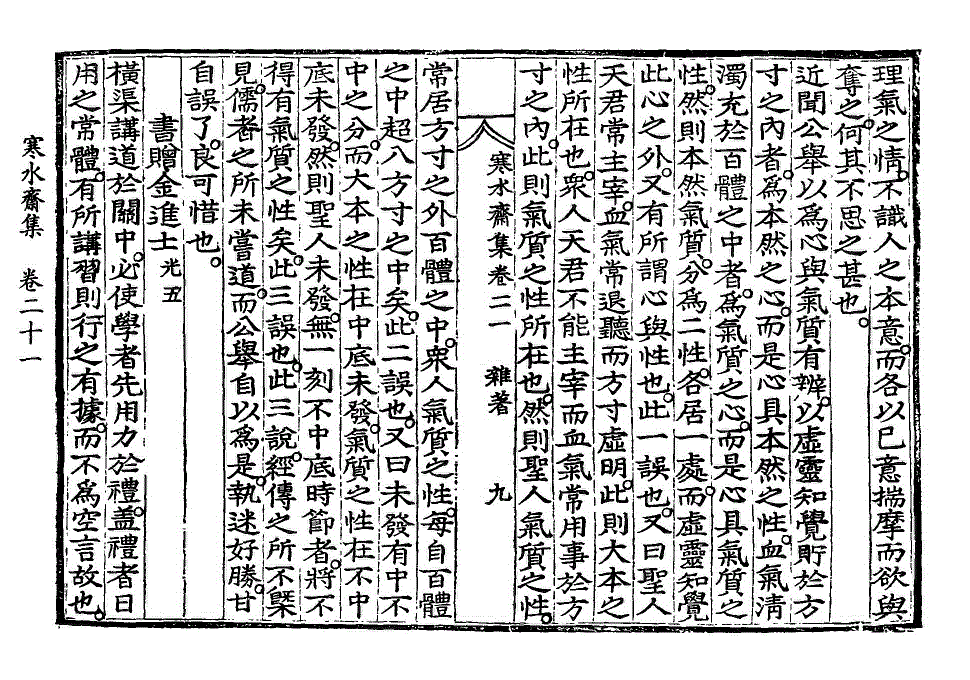 理气之情。不识人之本意。而各以己意揣摩而欲与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理气之情。不识人之本意。而各以己意揣摩而欲与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近闻公举以为心与气质有辨。以虚灵知觉贮于方寸之内者。为本然之心。而是心具本然之性。血气清浊充于百体之中者。为气质之心。而是心具气质之性。然则本然气质。分为二性。各居一处。而虚灵知觉此心之外。又有所谓心与性也。此一误也。又曰圣人天君常主宰。血气常退听而方寸虚明。此则大本之性所在也。众人天君不能主宰而血气常用事于方寸之内。此则气质之性所在也。然则圣人气质之性。常居方寸之外百体之中。众人气质之性。每自百体之中超入方寸之中矣。此二误也。又曰未发有中不中之分。而大本之性在中底未发。气质之性在不中底未发。然则圣人未发。无一刻不中底时节者。将不得有气质之性矣。此三误也。此三说。经传之所不槩见。儒者之所未尝道。而公举自以为是。执迷好胜。甘自误了。良可惜也。
书赠金进士(光五)
横渠讲道于关中。必使学者先用力于礼。盖礼者曰用之常体。有所讲习则行之有据。而不为空言故也。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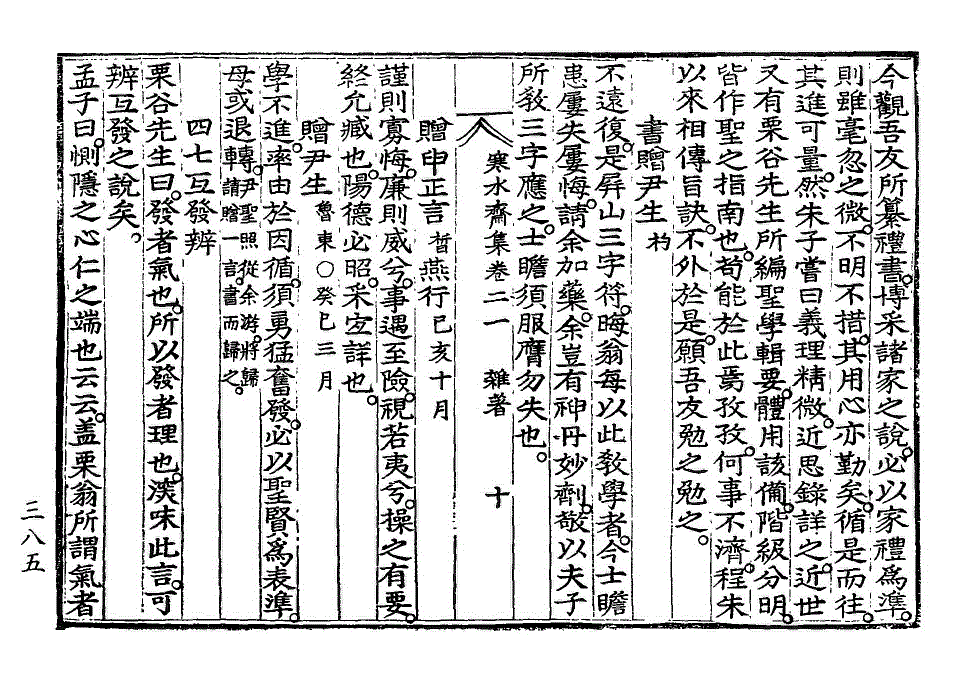 今观吾友所纂礼书。博采诸家之说。必以家礼为准。则虽毫忽之微。不明不措。其用心亦勤矣。循是而往。其进可量。然朱子尝曰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近世又有栗谷先生所编圣学辑要。体用该备。阶级分明。皆作圣之指南也。苟能于此焉孜孜。何事不济。程朱以来相传旨诀。不外于是。愿吾友勉之勉之。
今观吾友所纂礼书。博采诸家之说。必以家礼为准。则虽毫忽之微。不明不措。其用心亦勤矣。循是而往。其进可量。然朱子尝曰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近世又有栗谷先生所编圣学辑要。体用该备。阶级分明。皆作圣之指南也。苟能于此焉孜孜。何事不济。程朱以来相传旨诀。不外于是。愿吾友勉之勉之。书赠尹生(杓)
不远复。是屏山三字符。晦翁每以此教学者。今士瞻患屡失屡悔。请余加药。余岂有神丹妙剂。敬以夫子所教三字应之。士瞻须服膺勿失也。
赠申正言(晰)燕行(己亥十月)
谨则寡悔。廉则威兮。事遇至险。视若夷兮。操之有要。终允臧也。阳德必昭。采宜详也。
赠尹生(鲁东癸巳三月)
学不进。率由于因循。须勇猛奋发。必以圣贤为表准。母或退转。(尹圣照从余游。将归请赠一言。书而归之。)
四七互发辨
栗谷先生曰。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深味此言。可辨互发之说矣。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云云。盖栗翁所谓气者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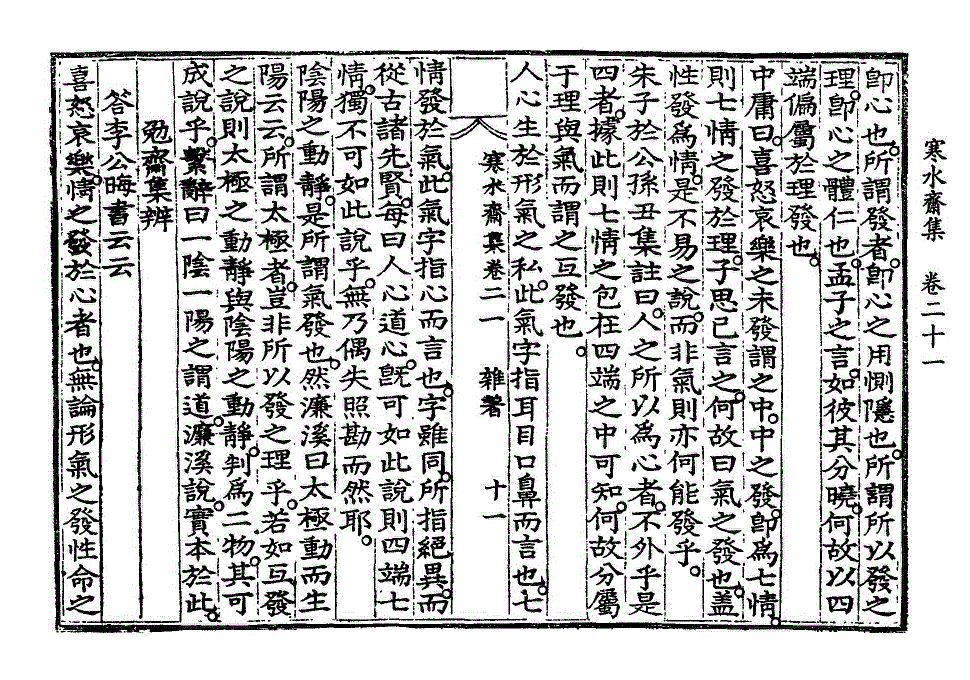 即心也。所谓发者。即心之用恻隐也。所谓所以发之理。即心之体仁也。孟子之言。如彼其分晓。何故以四端偏属于理发也。
即心也。所谓发者。即心之用恻隐也。所谓所以发之理。即心之体仁也。孟子之言。如彼其分晓。何故以四端偏属于理发也。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之发。即为七情。则七情之发于理。子思已言之。何故曰气之发也。盖性发为情。是不易之说。而非气则亦何能发乎。
朱子于公孙丑集注曰。人之所以为心者。不外乎是四者。据此则七情之包在四端之中可知。何故分属于理与气而谓之互发也。
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此气字指耳目口鼻而言也。七情发于气。此气字指心而言也。字虽同。所指绝异。而从古诸先贤。每曰人心道心。既可如此说则四端七情。独不可如此说乎。无乃偶失照勘而然耶。
阴阳之动静。是所谓气发也。然濂溪曰太极动而生阳云云。所谓太极者。岂非所以发之理乎。若如互发之说则太极之动静与阴阳之动静。判为二物。其可成说乎。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濂溪说。实本于此。
勉斋集辨
答李公晦书云云
喜怒哀乐。情之发于心者也。无论形气之发性命之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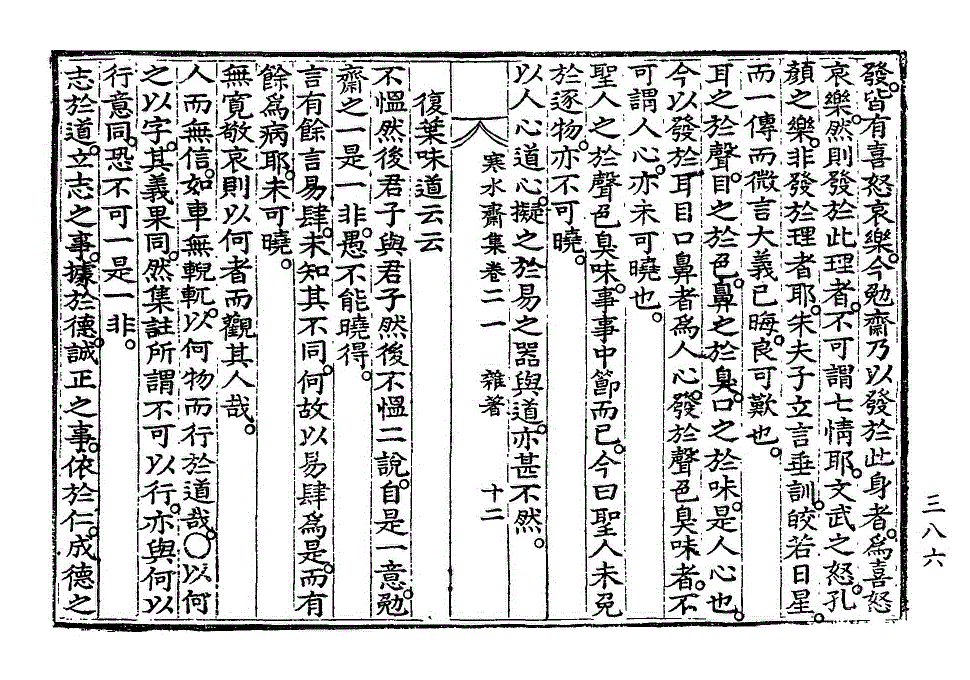 发。皆有喜怒哀乐。今勉斋乃以发于此身者。为喜怒哀乐。然则发于此理者。不可谓七情耶。文武之怒。孔颜之乐。非发于理者耶。朱夫子立言垂训。皎若日星。而一传而微言大义已晦。良可叹也。
发。皆有喜怒哀乐。今勉斋乃以发于此身者。为喜怒哀乐。然则发于此理者。不可谓七情耶。文武之怒。孔颜之乐。非发于理者耶。朱夫子立言垂训。皎若日星。而一传而微言大义已晦。良可叹也。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是人心也。今以发于耳目口鼻者为人心。发于声色臭味者。不可谓人心。亦未可晓也。
圣人之于声色臭味。事事中节而已。今曰圣人未免于逐物。亦不可晓。
以人心道心。拟之于易之器与道。亦甚不然。
复叶味道云云
不愠然后君子与君子然后不愠二说。自是一意。勉斋之一是一非。愚不能晓得。
言有馀言易肆。未知其不同。何故以易肆为是。而有馀为病耶。未可晓。
无宽敬哀则以何者而观其人哉。
人而无信。如车无輗軏。以何物而行于道哉。○以何之以字。其义果同。然集注所谓不可以行。亦与何以行意同。恐不可一是一非。
志于道。立志之事。据于德。诚正之事。依于仁。成德之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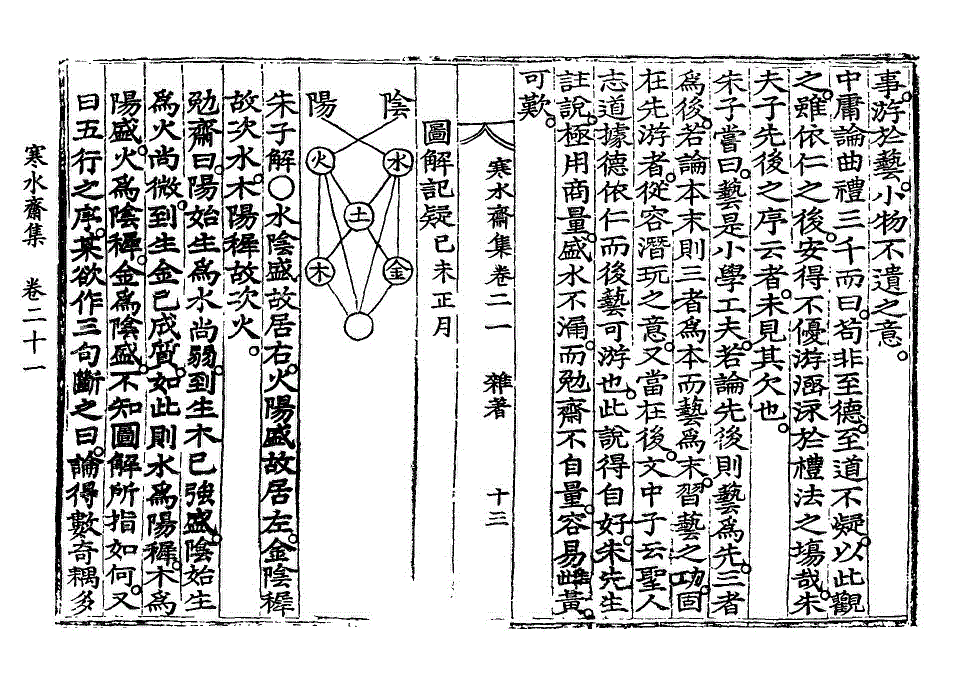 事。游于艺。小物不遗之意。
事。游于艺。小物不遗之意。中庸论曲礼三千而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以此观之。虽依仁之后。安得不优游涵泳于礼法之场哉。朱夫子先后之序云者。未见其欠也。
朱子尝曰。艺是小学工夫。若论先后则艺为先。三者为后。若论本末则三者为本而艺为末。习艺之功。固在先游者。从容潜玩之意。又当在后。文中子云圣人志道据德依仁而后艺可游也。此说得自好。朱先生注说。极用商量。盛水不漏。而勉斋不自量。容易雌黄。可叹。
图解记疑(己未正月)
삽화 새창열기
朱子解○水阴盛故居右。火阳盛故居左。金阴稚故次水。木阳稚故次火。
勉斋曰。阳始生为水尚弱。到生木已强盛。阴始生为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质。如此则水为阳稚。木为阳盛。火为阴稚。金为阴盛。不知圆解所指如何。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断之曰。论得数奇耦多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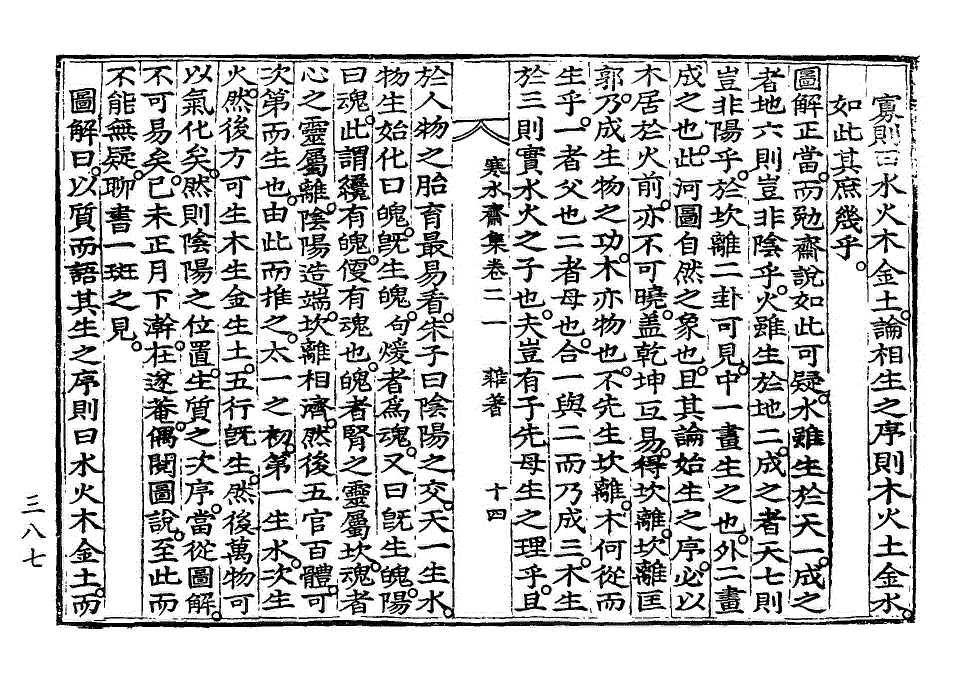 寡则曰水火木金土。论相生之序则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几乎。
寡则曰水火木金土。论相生之序则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几乎。图解正当。而勉斋说如此可疑。水虽生于天一。成之者地六则岂非阴乎。火虽生于地二。成之者天七则岂非阳乎。于坎离二卦可见。中一画生之也。外二画成之也。此河图自然之象也。且其论始生之序。必以木居于火前。亦不可晓。盖乾坤互易。得坎离。坎离匡郭。乃成生物之功。木亦物也。不先生坎离。木何从而生乎。一者父也二者母也。合一与二而乃成三。木生于三则实水火之子也。夫岂有子先母生之理乎。且于人物之胎育最易看。朱子曰阴阳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句煖者为魂。又曰既生魄。阳曰魂。此谓才有魄。便有魂也。魄者贤之灵属坎。魂者心之灵属离。阴阳造端。坎离相济。然后五官百体。可次第而生也。由此而推之。太一之初。第一生水。次生火。然后方可生木生金生土。五行既生。然后万物可以气化矣。然则阴阳之位置。生质之次序。当从图解。不可易矣。己未正月下浣。在遂庵。偶阅图说。至此而不能无疑。聊书一斑之见。
图解曰。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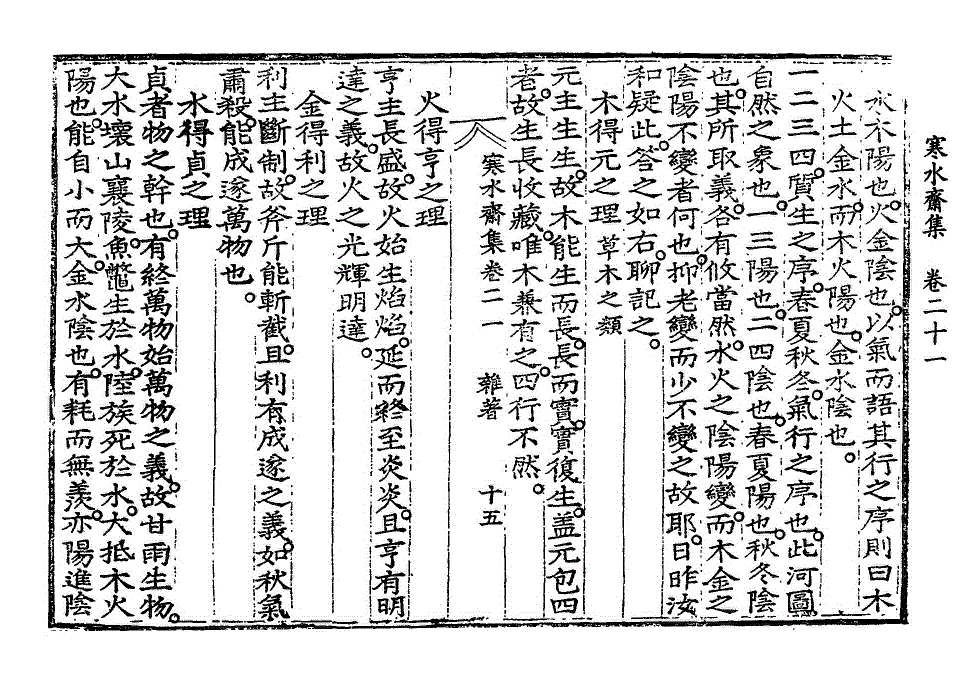 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
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一二三四。质生之序。春夏秋冬。气行之序也。此河图自然之象也。一三阳也。二四阴也。春夏阳也。秋冬阴也。其所取义。各有攸当然。水火之阴阳变。而木金之阴阳不变者何也。抑老变而少不变之故耶。日昨汝和疑此。答之如右。聊记之。
木得元之理(草木之类)
元主生生。故木能生而长。长而实。实复生。盖元包四者。故生长收藏。唯木兼有之。四行不然。
火得亨之理
亨主长盛。故火始生焰焰。延而终至炎炎。且亨有明达之义。故火之光辉明达。
金得利之理
利主断制。故斧斤能斩截。且利有成遂之义。如秋气肃杀。能成遂万物也。
水得贞之理
贞者物之干也。有终万物始万物之义。故甘雨生物。大水坏(一作怀)山襄陵。鱼鳖生于水。陆族死于水。大抵木火阳也。能自小而大。金水阴也。有耗而无羡。亦阳进阴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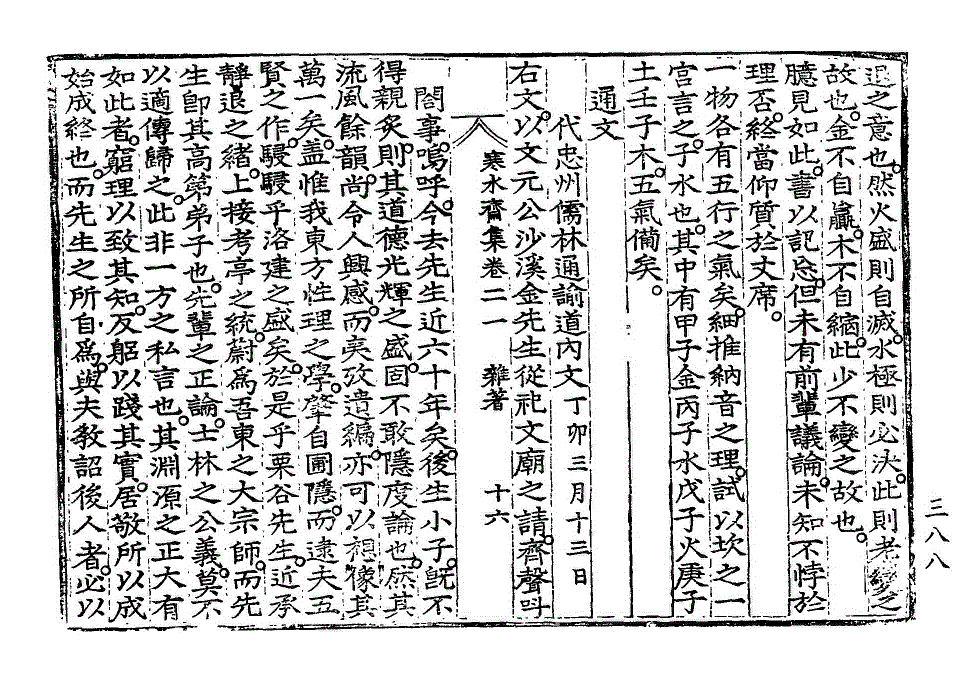 退之意也。然火盛则自灭。水极则必决。此则老变之故也。金不自赢。木不自缩。此少不变之故也。
退之意也。然火盛则自灭。水极则必决。此则老变之故也。金不自赢。木不自缩。此少不变之故也。臆见如此。书以记忘。但未有前辈议论。未知不悖于理否。终当仰质于文席。
一物各有五行之气矣。细推纳音之理。试以坎之一宫言之。子水也。其中有甲子金丙子水戊子火庚子土壬子木。五气备矣。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通文
代忠州儒林通谕道内文(丁卯三月十三日)
右文。以文元公沙溪金先生从祀文庙之请。齐声叫 閤事。呜呼。今去先生近六十年矣。后生小子。既不得亲灸。则其道德光辉之盛。固不敢隐度论也。然其流风馀韵。尚令人兴感。而夷考遗编。亦可以想像其万一矣。盖惟我东方性理之学。肇自圃隐。而逮夫五贤之作。骎骎乎洛建之盛矣。于是乎栗谷先生。近承静,退之绪。上接考亭之统。蔚为吾东之大宗师。而先生即其高第弟子也。先辈之正论。士林之公义(一作议)。莫不以适传归之。此非一方之私言也。其渊源之正大有如此者。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所以成始成终也。而先生之所自为。与夫教诏后人者。必以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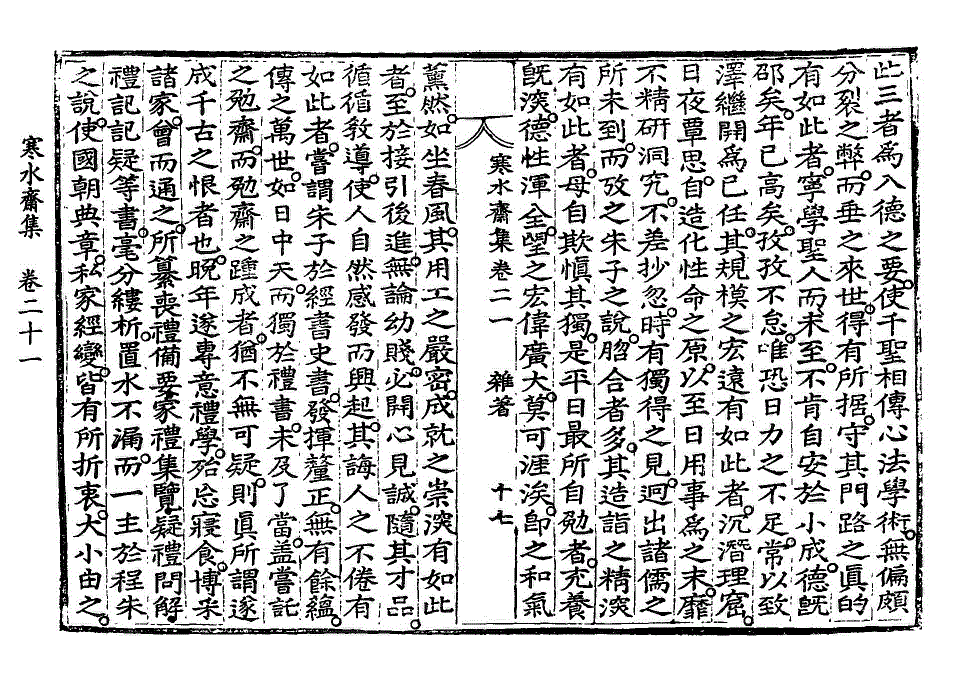 此三者为入德之要。使千圣相传心法学术。无偏颇分裂之弊。而垂之来世。得有所据。守其门路之真的有如此者。宁学圣人而未至。不肯自安于小成。德既邵矣。年已高矣。孜孜不怠。唯恐日力之不足。常以致泽继开为己任。其规模之宏远有如此者。沈潜理窟。日夜覃思。自造化性命之原。以至日用事为之末。靡不精研洞究。不差抄忽。时有独得之见。迥出诸儒之所未到。而考之朱子之说。吻合者多。其造诣之精深有如此者。毋自欺慎其独。是平曰最所自勉者。充养既深。德性浑全。望之宏伟广大。莫可涯涘。即之和气薰然。如坐春风。其用工之严密。成就之崇深有如此者。至于接引后进。无论幼贱。必开心见诚。随其才品。循循教导。使人自然感发而兴起。其诲人之不倦有如此者。尝谓朱子于经书史书。发挥釐正。无有馀蕴。传之万世。如日中天。而独于礼书。未及了当。盖尝托之勉斋。而勉斋之踵成者。犹不无可疑。则真所谓遂成千古之恨者也。晚年遂专意礼学。殆忘寝食。博采诸家。会而通之。所纂丧礼备要,家礼集览,疑礼问解,礼记记疑等书。毫分缕析。置水不漏。而一主于程朱之说。使国朝典章。私家经变。皆有所折衷。大小由之。
此三者为入德之要。使千圣相传心法学术。无偏颇分裂之弊。而垂之来世。得有所据。守其门路之真的有如此者。宁学圣人而未至。不肯自安于小成。德既邵矣。年已高矣。孜孜不怠。唯恐日力之不足。常以致泽继开为己任。其规模之宏远有如此者。沈潜理窟。日夜覃思。自造化性命之原。以至日用事为之末。靡不精研洞究。不差抄忽。时有独得之见。迥出诸儒之所未到。而考之朱子之说。吻合者多。其造诣之精深有如此者。毋自欺慎其独。是平曰最所自勉者。充养既深。德性浑全。望之宏伟广大。莫可涯涘。即之和气薰然。如坐春风。其用工之严密。成就之崇深有如此者。至于接引后进。无论幼贱。必开心见诚。随其才品。循循教导。使人自然感发而兴起。其诲人之不倦有如此者。尝谓朱子于经书史书。发挥釐正。无有馀蕴。传之万世。如日中天。而独于礼书。未及了当。盖尝托之勉斋。而勉斋之踵成者。犹不无可疑。则真所谓遂成千古之恨者也。晚年遂专意礼学。殆忘寝食。博采诸家。会而通之。所纂丧礼备要,家礼集览,疑礼问解,礼记记疑等书。毫分缕析。置水不漏。而一主于程朱之说。使国朝典章。私家经变。皆有所折衷。大小由之。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89L 页
 无所疑贰。则朱子之所恨者。至此而庶几无憾矣。且如经书辨疑,近思释疑等书。又可见讲明义理。羽翼经传之功矣。噫。我先生之德之功如彼其盛大。而朱子栗翁之道。赖而不坠。则斯可谓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师表。而从祀之 典。尚今寥寥。岂非 圣世之欠事。而斯文之至恨也耶。此论之发。盖已有年。前后陈章。亦非一二。而 圣意持难。尚未准请。多士郁抑。为如何哉。玆欲与道内诸君子。合辞陈疏。以期回 天。伏愿佥尊。趁某日齐会于某处。以为一时西上之地。千万幸甚。
无所疑贰。则朱子之所恨者。至此而庶几无憾矣。且如经书辨疑,近思释疑等书。又可见讲明义理。羽翼经传之功矣。噫。我先生之德之功如彼其盛大。而朱子栗翁之道。赖而不坠。则斯可谓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师表。而从祀之 典。尚今寥寥。岂非 圣世之欠事。而斯文之至恨也耶。此论之发。盖已有年。前后陈章。亦非一二。而 圣意持难。尚未准请。多士郁抑。为如何哉。玆欲与道内诸君子。合辞陈疏。以期回 天。伏愿佥尊。趁某日齐会于某处。以为一时西上之地。千万幸甚。崇贤书院通谕中外文
右文。为尤庵宋先生奉享于崇贤书院事。呜呼。惟我先生祸变之后。凡我后生小子之含忍痛冤。靡所依仰者六年于玆矣。何幸 天曰重明。 圣心快悟。既复其官爵矣。又遣近侍赐祭矣。又 命有司将举易名之典矣。凡所以昭雪冤枉。隐卒褒德者。无有馀憾矣。然则今玆俎豆明宫。以寓羹墙江汉之思者。其可以少缓乎。呜呼。先生生朱子数百载之后。乃能由溪门而溯石潭。由石潭而溯朱子。使朱子之道。焕然大明于后世。则虽道大难容。未究其用。而其辟邪放淫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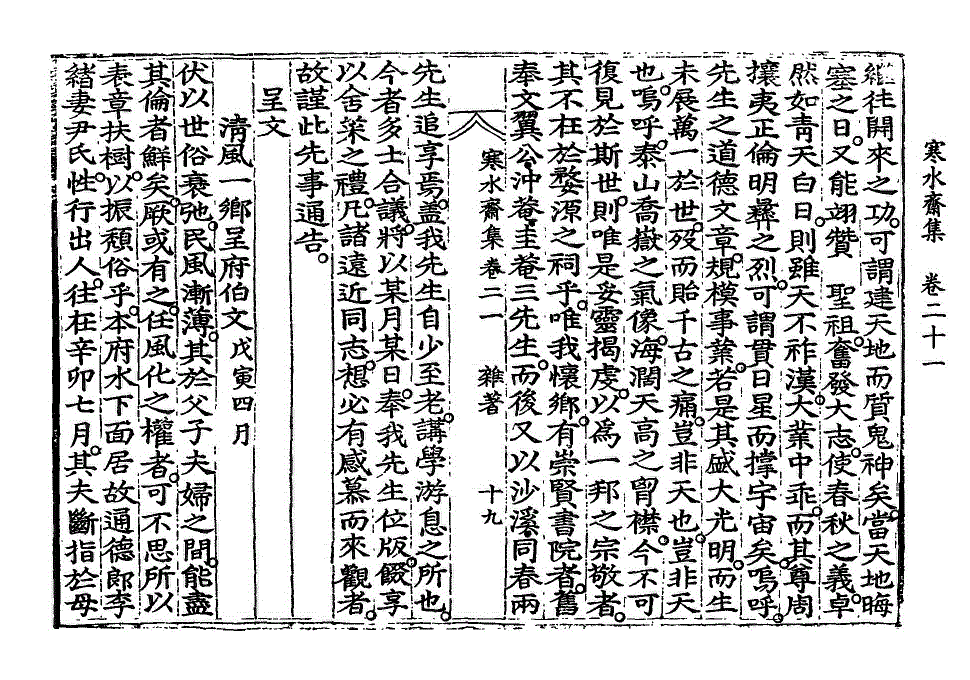 继往开来之功。可谓建天地而质鬼神矣。当天地晦塞之日。又能翊赞 圣祖。奋发大志。使春秋之义。卓然如青天白日。则虽天不祚汉。大业中乖。而其尊周攘夷正伦明彝之烈。可谓贯日星而撑宇宙矣。呜呼。先生之道德文章。规模事业。若是其盛大光明。而生未展万一于世。殁而贻千古之痛。岂非天也。岂非天也。呜呼。泰山乔岳之气像。海阔天高之胸襟。今不可复见于斯世。则唯是妥灵揭虔。以为一邦之宗敬者。其不在于婺源之祠乎。唯我怀乡。有崇贤书院者。旧奉文翼公,冲庵,圭庵三先生。而后又以沙溪,同春两先生追享焉。盖我先生自少至老。讲学游息之所也。今者多士合议。将以某月某日。奉我先生位版。啜享以舍菜之礼。凡诸远近同志。想必有感慕而来观者。故谨此先事通告。
继往开来之功。可谓建天地而质鬼神矣。当天地晦塞之日。又能翊赞 圣祖。奋发大志。使春秋之义。卓然如青天白日。则虽天不祚汉。大业中乖。而其尊周攘夷正伦明彝之烈。可谓贯日星而撑宇宙矣。呜呼。先生之道德文章。规模事业。若是其盛大光明。而生未展万一于世。殁而贻千古之痛。岂非天也。岂非天也。呜呼。泰山乔岳之气像。海阔天高之胸襟。今不可复见于斯世。则唯是妥灵揭虔。以为一邦之宗敬者。其不在于婺源之祠乎。唯我怀乡。有崇贤书院者。旧奉文翼公,冲庵,圭庵三先生。而后又以沙溪,同春两先生追享焉。盖我先生自少至老。讲学游息之所也。今者多士合议。将以某月某日。奉我先生位版。啜享以舍菜之礼。凡诸远近同志。想必有感慕而来观者。故谨此先事通告。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呈文
清风一乡呈府伯文(戊寅四月)
伏以世俗衰弛。民风渐薄。其于父子夫妇之间。能尽其伦者鲜矣。厥或有之。任风化之权者。可不思所以表章扶树。以振颓俗乎。本府水下面居故通德郎李绪妻尹氏。性行出人。往在辛卯七月。其夫断指于母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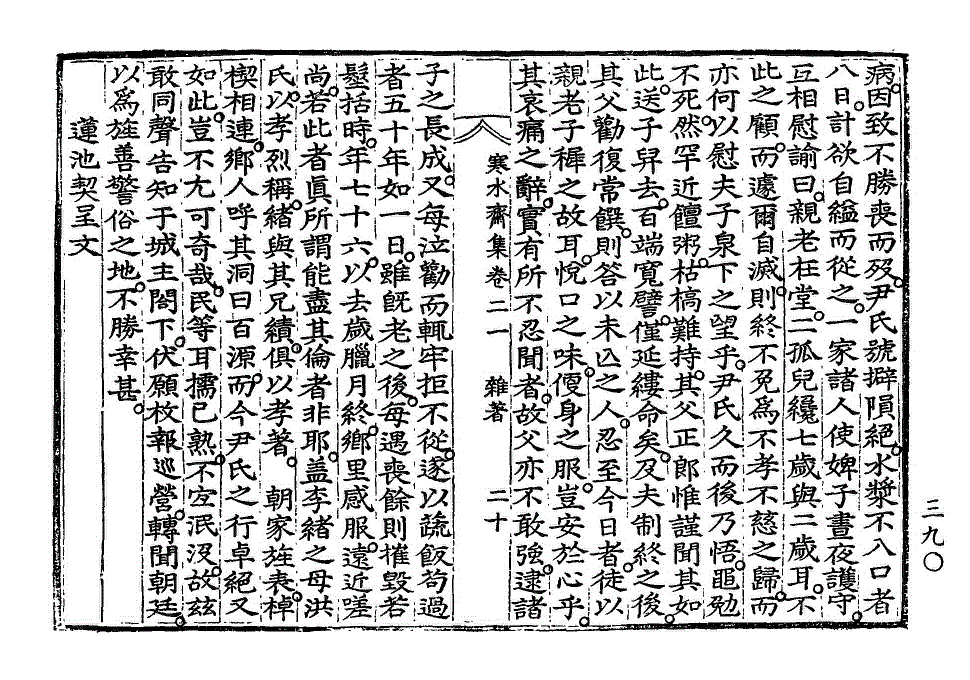 病。因致不胜丧而殁。尹氏号擗陨绝。水浆不入口者八日。计欲自缢而从之。一家诸人使婢子昼夜护守。互相慰谕曰。亲老在堂。二孤儿才七岁与二岁耳。不此之顾。而遽尔自灭。则终不免为不孝不慈之归。而亦何以慰夫子泉下之望乎。尹氏久而后乃悟。黾勉不死。然罕近饘粥。枯槁难持。其父正郎惟谨闻其如此。送子舁去。百端宽譬。仅延缕命矣。及夫制终之后。其父劝复常馔。则答以未亡之人。忍至今日者。徒以亲老子稚之故耳。悦口之味。便身之服。岂安于心乎。其哀痛之辞。实有所不忍闻者。故父亦不敢强。逮诸子之长成。又每泣劝而辄牢拒不从。遂以蔬饭苟过者五十年如一日。虽既老之后。每遇丧馀则摧毁若髽括时。年七十六。以去岁腊月终。乡里感服。远近嗟尚。若此者真所谓能尽其伦者非耶。盖李绪之母洪氏。以孝烈称。绪与其兄绩。俱以孝著。 朝家旌表。棹楔相连。乡人呼其洞曰百源。而今尹氏之行卓绝又如此。岂不尤可奇哉。民等耳擩已熟。不宜泯没。故玆敢同声告知于城主閤下。伏愿枚报巡营。转闻朝廷。以为旌善警俗之地。不胜幸甚。
病。因致不胜丧而殁。尹氏号擗陨绝。水浆不入口者八日。计欲自缢而从之。一家诸人使婢子昼夜护守。互相慰谕曰。亲老在堂。二孤儿才七岁与二岁耳。不此之顾。而遽尔自灭。则终不免为不孝不慈之归。而亦何以慰夫子泉下之望乎。尹氏久而后乃悟。黾勉不死。然罕近饘粥。枯槁难持。其父正郎惟谨闻其如此。送子舁去。百端宽譬。仅延缕命矣。及夫制终之后。其父劝复常馔。则答以未亡之人。忍至今日者。徒以亲老子稚之故耳。悦口之味。便身之服。岂安于心乎。其哀痛之辞。实有所不忍闻者。故父亦不敢强。逮诸子之长成。又每泣劝而辄牢拒不从。遂以蔬饭苟过者五十年如一日。虽既老之后。每遇丧馀则摧毁若髽括时。年七十六。以去岁腊月终。乡里感服。远近嗟尚。若此者真所谓能尽其伦者非耶。盖李绪之母洪氏。以孝烈称。绪与其兄绩。俱以孝著。 朝家旌表。棹楔相连。乡人呼其洞曰百源。而今尹氏之行卓绝又如此。岂不尤可奇哉。民等耳擩已熟。不宜泯没。故玆敢同声告知于城主閤下。伏愿枚报巡营。转闻朝廷。以为旌善警俗之地。不胜幸甚。莲池契呈文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1H 页
 云云。本契盘石坊故学生赵圣佐妻权氏。承义副尉尚友之女也。天禀仁孝。其在幼年。尽礼于母丧。其父鳏居。竭诚奉养。岁庚申年十九而嫁。夫党莫不服其懿行。逮至辛酉冬。其夫重得奇疾。其父所患亦方沈剧。一室之内。两病滨危。权氏不解带不交睫。夙夜拥炉。亲尝药饵。怀妊满朔。不少自恤。严冬处冷。不暂休息。妆奁衣服。尽归药债。病人不食。亦不进食。似此吃苦。经年如一日。壬戌三月。权氏解㝃得男。而屏其儿不见曰。吾若眷恋此儿。救病不专一。即日起行。未几其夫不淑。权氏有自经之计。瞰人之无。就殡系颈。为家人所觉。几殊而乃稣。诸父闷其然也。诡辞绐之曰。自决便是凶终。如是者不得与其夫同穴。权氏对曰儿实妄矣。今日拟决死。自此谨奉教。仍自怀中出五六幅谚书。俾纳于其夫棺中。盖皆誓死之言也。才过成服。其父继殁。自此死志益坚。频自踬于堂下丈馀地。百体碎伤。胁骨中折。粒米不入口。盖其意若不致伤而死则必欲因饿而自尽也。自初终以后。不离丧次。哭不绝声。委伏苫垩。不脱衰绖。挥却溢糜。俾不近前。只以冷水润喉。以继哭泣。邻里不忍闻其声。至欲避去。行路亦为之流涕。远近皆称曰孝哉此女。烈哉
云云。本契盘石坊故学生赵圣佐妻权氏。承义副尉尚友之女也。天禀仁孝。其在幼年。尽礼于母丧。其父鳏居。竭诚奉养。岁庚申年十九而嫁。夫党莫不服其懿行。逮至辛酉冬。其夫重得奇疾。其父所患亦方沈剧。一室之内。两病滨危。权氏不解带不交睫。夙夜拥炉。亲尝药饵。怀妊满朔。不少自恤。严冬处冷。不暂休息。妆奁衣服。尽归药债。病人不食。亦不进食。似此吃苦。经年如一日。壬戌三月。权氏解㝃得男。而屏其儿不见曰。吾若眷恋此儿。救病不专一。即日起行。未几其夫不淑。权氏有自经之计。瞰人之无。就殡系颈。为家人所觉。几殊而乃稣。诸父闷其然也。诡辞绐之曰。自决便是凶终。如是者不得与其夫同穴。权氏对曰儿实妄矣。今日拟决死。自此谨奉教。仍自怀中出五六幅谚书。俾纳于其夫棺中。盖皆誓死之言也。才过成服。其父继殁。自此死志益坚。频自踬于堂下丈馀地。百体碎伤。胁骨中折。粒米不入口。盖其意若不致伤而死则必欲因饿而自尽也。自初终以后。不离丧次。哭不绝声。委伏苫垩。不脱衰绖。挥却溢糜。俾不近前。只以冷水润喉。以继哭泣。邻里不忍闻其声。至欲避去。行路亦为之流涕。远近皆称曰孝哉此女。烈哉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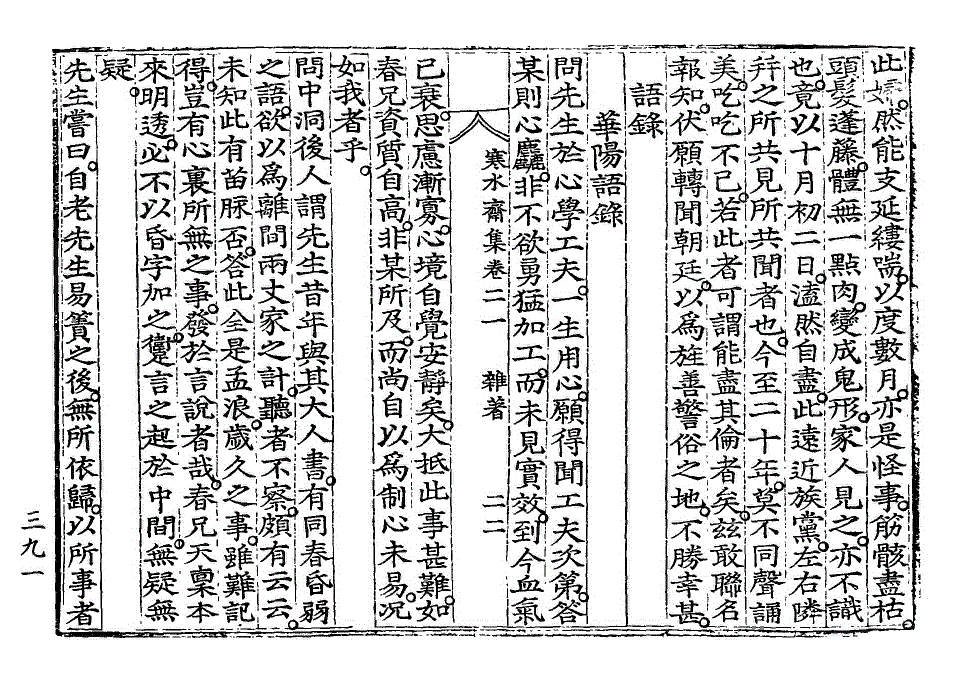 此妇。然能支延缕喘。以度数月。亦是怪事。筋骸尽枯。头发蓬藤。体无一点肉。变成鬼形。家人见之。亦不识也。竟以十月初二日。溘然自尽。此远近族党。左右邻并之所共见所共闻者也。今至二十年。莫不同声诵美。吃吃不已。若此者可谓能尽其伦者矣。玆敢联名报知。伏愿转闻朝廷。以为旌善警俗之地。不胜幸甚。
此妇。然能支延缕喘。以度数月。亦是怪事。筋骸尽枯。头发蓬藤。体无一点肉。变成鬼形。家人见之。亦不识也。竟以十月初二日。溘然自尽。此远近族党。左右邻并之所共见所共闻者也。今至二十年。莫不同声诵美。吃吃不已。若此者可谓能尽其伦者矣。玆敢联名报知。伏愿转闻朝廷。以为旌善警俗之地。不胜幸甚。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语录
华阳语录
问先生于心学工夫。一生用心。愿得闻工夫次第。答某则心粗。非不欲勇猛加工。而未见实效。到今血气已衰。思虑渐寡。心境自觉安静矣。大抵此事甚难。如春兄资质自高。非某所及。而尚自以为制心未易。况如我者乎。
问中洞后人谓先生昔年与其大人书。有同春昏弱之语。欲以为离间两丈家之计。听者不察。颇有云云。未知此有苗脉否。答此全是孟浪。岁久之事。虽难记得。岂有心里所无之事。发于言说者哉。春兄天禀本来明透。必不以昏字加之。躗言之起于中间。无疑无疑。
先生尝曰。自老先生易箦之后。无所依归。以所事者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2H 页
 事慎斋。欲为卒业之地。而终未有得。至于侪友则无大段得力处。而只于同春资益最多。若文字则侪友或不能无资于我矣。
事慎斋。欲为卒业之地。而终未有得。至于侪友则无大段得力处。而只于同春资益最多。若文字则侪友或不能无资于我矣。己巳行中语录
南迁 命下后。亲旧之来慰者。皆曰时事可惊。则先生辄应曰知有此事久矣。何足惊也。
先生曰。东坡谴谪时答友人书。则以谈笑自若相勉。而自家反不免遗尿。始知血气之勇。终难得力也。又曰东披是客气。刘元城是正气也。
先生曰。少时常愿读书决科。得以海路朝 天。则长风破浪。快豁心胸矣。今行得谐此愿。幸也。然一上汉拿山。亦所愿也。而去作围中之人。无由获遂。是可恨也。客有曰先生虽越海。不久当还渡。更拜可期。先生不答。莞尔而笑。
先生闻济州之 命曰。金吾郎未到之前。不妨拜辞于家庙。遂冒夜往来苏堤。(先生时在兴农)
亲旧拜别时。或有垂涕者。则先生曰朱先生之别西山也。不见嗟劳色。何不法此而乃尔也。
先生过连山。欲入拜遁岩书院。更思曰程子涪行。请见叔母则朱子不满于心。遂遣郑游。操文替告于沙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2L 页
 溪墓前。
溪墓前。砺山时构劄疑序文授尚夏曰。从今君与仲和。商量修改。对曰疑处当以问目呈禀。曰不须尔也。吾衰甚矣。虽自照管。每患误勘。君二人直可相议梳洗。有何疑难。尚夏曰小小处谨当如戒。至于关系重大。有难自断处。敢不具禀。先生颔之。尚夏曰。仲和之安居讲论不可必。若尔则如之何。先生曰同甫颇详密。可与之相议也。金沟时先生问曰。鑴之罪何事最大。尚夏对曰谋逆之罪最大。先生微笑而言曰。君之穷理工夫未深矣。尚夏曰然则凌侮朱子是最大罪乎。先生点头曰然。人苟凌侮圣贤则何事不为乎。
先生谓尚夏曰。诸友虽散。君则不可不又偕我数日。吾有从容欲语者矣。至泰仁留一日。鸡鸣起寝。尚夏侍坐。先生曰栗谷先生手迹颇多。(如石潭日记之类)又有沙溪先生与白沙李公删定栗翁碑文时。往复文字及行状草本。慎斋裒稡深藏。至末年传授于我矣。今我作此行。托与致道。自我言之则如此说及。实有未安者矣。然致道其勉守之。栗翁子孙设欲持去。此异于他物。不可与也。吾初欲与朴和叔共守之。今和叔如彼奈何。尚夏曰今日小生。亦安保其无恙在家耶。若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3H 页
 尔则将置此物于何处。先生曰吾观君之胤子上舍非等閒人物。且君家深僻。保无忧也。他日畴孙生还则与之共守。亦不妨也。又曰二程全书分类。欲与君议定凡例。送置浮本于华阳矣。归时可取去修正也。其见于近思录及语类者。并采朱子说叶氏注。载录于本条之下亦好矣。可商量为之。又曰语类小分在兴溪架上。可取去检校。又曰退溪书吾始作劄疑。才到一卷。致道须卒业。以成吾志。尚夏辞谢。则曰此于君无难。勉旃勉旃。
尔则将置此物于何处。先生曰吾观君之胤子上舍非等閒人物。且君家深僻。保无忧也。他日畴孙生还则与之共守。亦不妨也。又曰二程全书分类。欲与君议定凡例。送置浮本于华阳矣。归时可取去修正也。其见于近思录及语类者。并采朱子说叶氏注。载录于本条之下亦好矣。可商量为之。又曰语类小分在兴溪架上。可取去检校。又曰退溪书吾始作劄疑。才到一卷。致道须卒业。以成吾志。尚夏辞谢。则曰此于君无难。勉旃勉旃。先生又曰君与市南家分谊之深。吾所知也。须顾护其子孙。尚夏对曰以顾护为托则小生不敢当。而教意何敢忘。
及乘海船。长吟东坡九死南荒吾不恨。玆游奇绝冠平生之句。(此条闻于叙九)
楚山语录
己巳六月初八日卯时。尚夏与君平偕入。先生气息奄奄。若不支顷刻。开眼视尚夏。握手而教曰。余尝以朝闻夕死为冀。今年踰八十而终于无所闻而死。是吾恨也。此时生不如死。吾则含笑入地矣。此后唯恃致道。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3L 页
 问后事当用何礼。答用丧礼备要。然大要以家礼为主。而其未备者以备要参用。
问后事当用何礼。答用丧礼备要。然大要以家礼为主。而其未备者以备要参用。问先生此时异于平日。公服用之否。先生掉头曰吾平日虽或造朝。每借他人公服。未尝有自制之事矣。问当用深衣。而其次用何服。答朱子致仕閒居。著上衣下裳之服。故吾尝仿此制而制置矣。问于家人而觅用。问其次用何服。答襕衫是 皇明太祖时所崇用也。用此可也。
先生曰学问当主朱子。事业则以 孝庙所欲为之志为主。我国国小力弱。纵不能有所为。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诸胸中。同志之士。传守勿失可也。
曰朱子学问。致知存养。实践(力行在其中)扩充。(治平在其中)而敬则通贯始终。勉斋所作行状详矣。
又曰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应万事。直而已。孔孟以来相传。唯是一直字。而朱子临终告门人。亦不外此。君其勉之。
曰昔人于复 昭陵时。何不先以复 贞陵为请也。吾之立朝所为者。唯此复 贞陵一事。庶可有辞矣。仍指权以镇而言曰。闻此儿之言。其梦兆真是奇事。
寒水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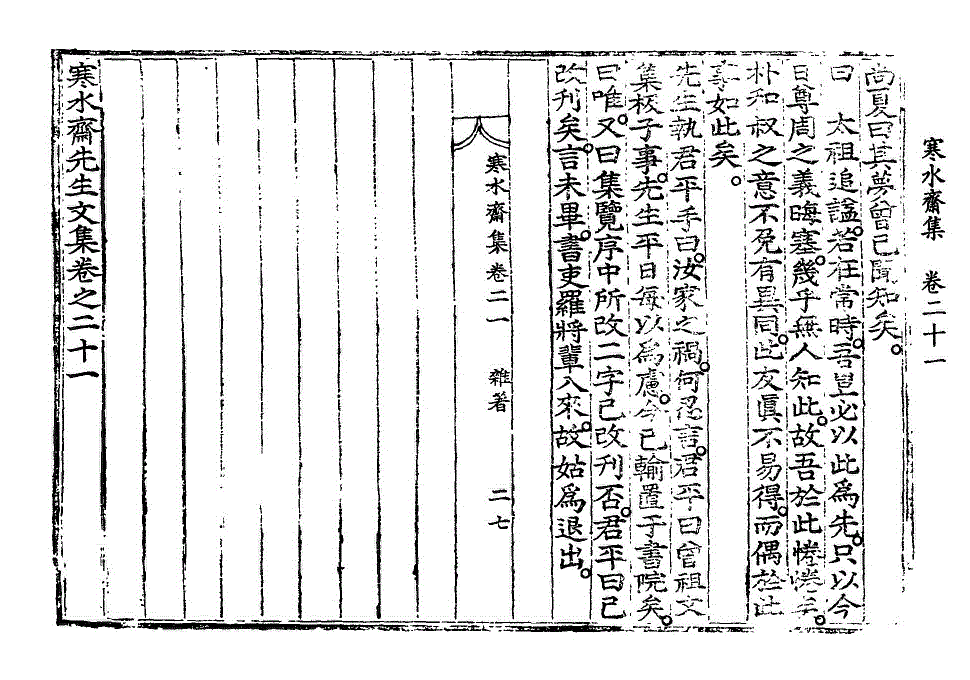 尚夏曰其梦曾已闻知矣。
尚夏曰其梦曾已闻知矣。曰 太祖追谥。若在常时。吾岂必以此为先。只以今日尊周之义晦塞。几乎无人知此。故吾于此惓惓矣。朴和叔之意不免有异同。此友真不易得。而偶于此事如此矣。
先生执君平手曰。汝家之祸。何忍言。君平曰曾祖文集板子事。先生平日每以为虑。今已输置于书院矣。曰唯。又曰集览序中所改二字已改刊否。君平曰已改刊矣。言未毕。书吏罗将辈入来。故姑为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