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x 页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筵奏
筵奏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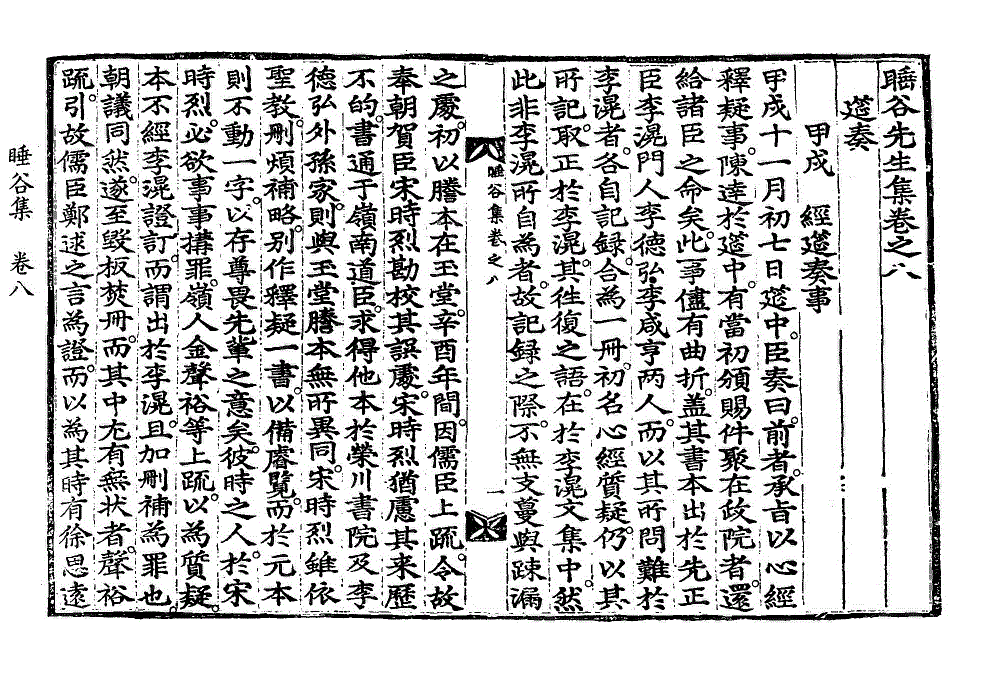 甲戌 经筵奏事
甲戌 经筵奏事甲戌十一月初七日筵中。臣奏曰。前者。承旨以心经释疑事。陈达于筵中。有当初颁赐件聚在政院者。还给诸臣之命矣。此事尽有曲折。盖其书本出于先正臣李滉门人李德弘,李咸亨两人。而以其所问难于李滉者。各自记录。合为一册。初名心经质疑。仍以其所记。取正于李滉。其往复之语。在于李滉文集中。然此非李滉所自为者。故记录之际。不无支蔓与疏漏之处。初以誊本在玉堂。辛酉年间。因儒臣上疏。令故奉朝贺臣宋时烈勘校其误处。宋时烈犹虑其来历不的。书通于岭南道臣。求得他本于荣川书院及李德弘外孙家。则与玉堂誊本无所异同。宋时烈虽依圣教。删烦补略。别作释疑一书。以备睿览。而于元本则不动一字。以存尊畏先辈之意矣。彼时之人。于宋时烈。必欲事事搆罪。岭人金声裕等上疏。以为质疑。本不经李滉證订。而谓出于李滉。且加删补为罪也。朝议同然。遂至毁板焚册。而其中尤有无状者。声裕疏。引故儒臣郑逑之言为證。而以为其时有徐思远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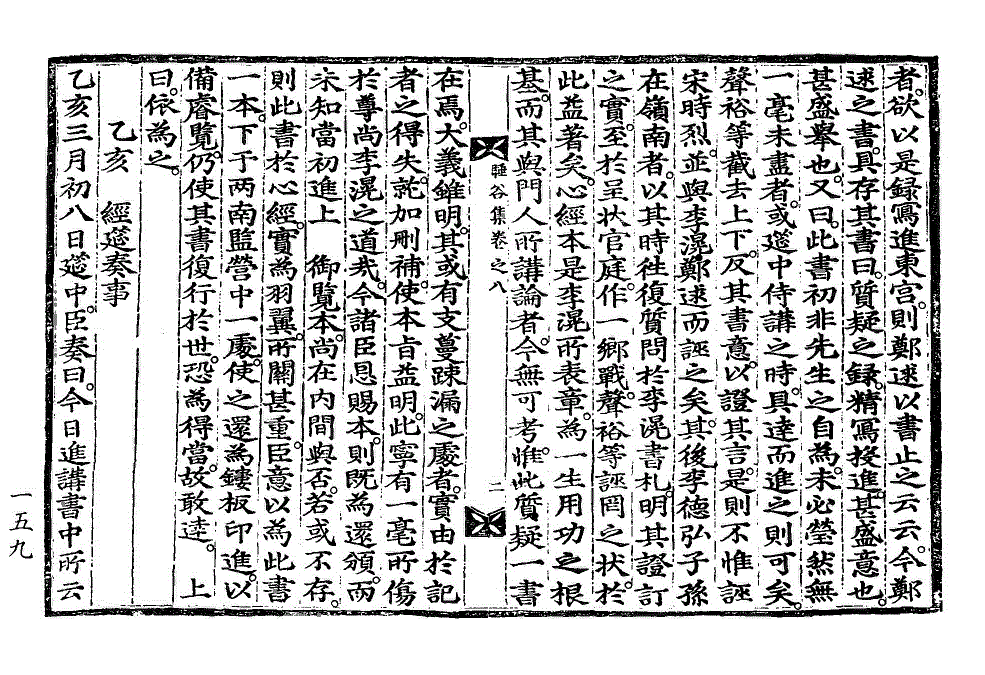 者。欲以是录写进东宫。则郑逑以书止之云云。今郑逑之书。具存其书曰。质疑之录。精写投进。甚盛意也。甚盛举也。又曰。此书初非先生之自为。未必莹然无一毫未尽者。或筵中侍讲之时。具达而进之则可矣。声裕等截去上下。反其书意。以證其言。是则不惟诬宋时烈。并与李滉,郑逑而诬之矣。其后李德弘子孙在岭南者。以其时往复质问于李滉书札。明其證订之实。至于呈状官庭。作一乡战。声裕等诬罔之状。于此益著矣。心经本是李滉所表章。为一生用功之根基。而其与门人所讲论者。今无可考。惟此质疑一书在焉。大义虽明。其或有支蔓疏漏之处者。实由于记者之得失。就加删补。使本旨益明。此宁有一毫所伤于尊尚李滉之道哉。今诸臣恩赐本。则既为还颁。而未知当初进上 御览本。尚在内间与否。若或不存。则此书于心经。实为羽翼。所关甚重。臣意以为此书一本。下于两南监营中一处。使之还为镂板印进。以备睿览。仍使其书复行于世。恐为得当。故敢达。 上曰。依为之。
者。欲以是录写进东宫。则郑逑以书止之云云。今郑逑之书。具存其书曰。质疑之录。精写投进。甚盛意也。甚盛举也。又曰。此书初非先生之自为。未必莹然无一毫未尽者。或筵中侍讲之时。具达而进之则可矣。声裕等截去上下。反其书意。以證其言。是则不惟诬宋时烈。并与李滉,郑逑而诬之矣。其后李德弘子孙在岭南者。以其时往复质问于李滉书札。明其證订之实。至于呈状官庭。作一乡战。声裕等诬罔之状。于此益著矣。心经本是李滉所表章。为一生用功之根基。而其与门人所讲论者。今无可考。惟此质疑一书在焉。大义虽明。其或有支蔓疏漏之处者。实由于记者之得失。就加删补。使本旨益明。此宁有一毫所伤于尊尚李滉之道哉。今诸臣恩赐本。则既为还颁。而未知当初进上 御览本。尚在内间与否。若或不存。则此书于心经。实为羽翼。所关甚重。臣意以为此书一本。下于两南监营中一处。使之还为镂板印进。以备睿览。仍使其书复行于世。恐为得当。故敢达。 上曰。依为之。乙亥 经筵奏事
乙亥三月初八日筵中。臣奏曰。今日进讲书中所云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0H 页
 一言之过。贻害将不胜救者。臣则以为 圣上即今正宜体念也。日者。大司谏臣洪受瀗疏。批于群下。疑惧之端。反覆晓谕。在廷臣僚。孰不感激。而其中台 启准请之后。不无层加之论一款。又与群下本情。万万相反。伏闻其后。又于筵中。因谏臣陈白。已有开释之教。然小臣之意以为 圣上既知群情之不然。而此特出于一时偶发之教。则所下批旨中。须即删改。方可以解四方之惑。而使群下得安也。当初 圣上处分严急。大小惴慄。恐或转至于过差。群臣本意。惟思随事极力以争。不惟大臣所虑为然。三司诸臣于此。孰不皆然。此举国之同情。而今者 圣教。反以三司之论。致疑于不敢言之地。有此下教。若仍存不改。则群下何得自容。以立朝事君乎。此事关系不轻。故臣惶恐敢达矣。 上曰。予意顷已备悉于筵中。而筵臣所达又如此。批答中层加之议等字删改。可也。○臣新从外来。敢陈民间事状矣。上年圻甸农事。未免失稔。而国家布施大惠。特减大同米一等。即今圻民得免填壑之患者。寔赖于此矣。第秋后雹灾之酷。曾所未有其雹灾所过。则田畴荡然无一所收。故被灾尤甚之处。殆过于辛亥。其中无产业之类。则率皆流离。
一言之过。贻害将不胜救者。臣则以为 圣上即今正宜体念也。日者。大司谏臣洪受瀗疏。批于群下。疑惧之端。反覆晓谕。在廷臣僚。孰不感激。而其中台 启准请之后。不无层加之论一款。又与群下本情。万万相反。伏闻其后。又于筵中。因谏臣陈白。已有开释之教。然小臣之意以为 圣上既知群情之不然。而此特出于一时偶发之教。则所下批旨中。须即删改。方可以解四方之惑。而使群下得安也。当初 圣上处分严急。大小惴慄。恐或转至于过差。群臣本意。惟思随事极力以争。不惟大臣所虑为然。三司诸臣于此。孰不皆然。此举国之同情。而今者 圣教。反以三司之论。致疑于不敢言之地。有此下教。若仍存不改。则群下何得自容。以立朝事君乎。此事关系不轻。故臣惶恐敢达矣。 上曰。予意顷已备悉于筵中。而筵臣所达又如此。批答中层加之议等字删改。可也。○臣新从外来。敢陈民间事状矣。上年圻甸农事。未免失稔。而国家布施大惠。特减大同米一等。即今圻民得免填壑之患者。寔赖于此矣。第秋后雹灾之酷。曾所未有其雹灾所过。则田畴荡然无一所收。故被灾尤甚之处。殆过于辛亥。其中无产业之类。则率皆流离。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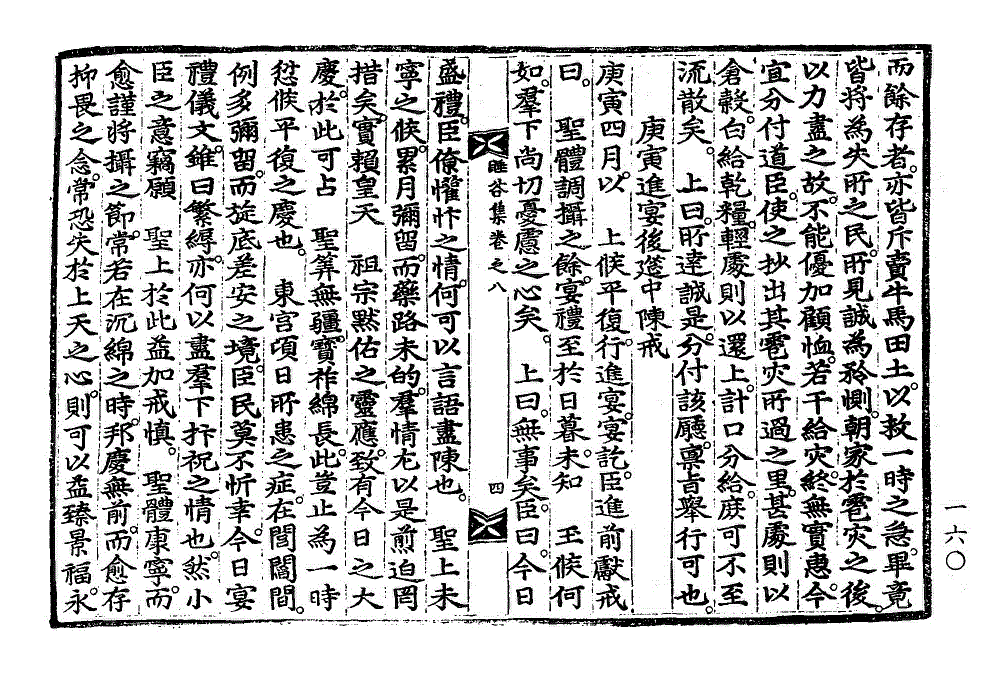 而馀存者。亦皆斥卖牛马田土。以救一时之急。毕竟皆将为失所之民。所见诚为矜恻。朝家于雹灾之后。以力尽之故。不能优加顾恤。若干给灾。终无实惠。今宜分付道臣。使之抄出其雹灾所过之里。甚处则以仓谷。白给乾粮。轻处则以还上。计口分给。庶可不至流散矣。 上曰。所达诚是。分付该厅。禀旨举行可也。
而馀存者。亦皆斥卖牛马田土。以救一时之急。毕竟皆将为失所之民。所见诚为矜恻。朝家于雹灾之后。以力尽之故。不能优加顾恤。若干给灾。终无实惠。今宜分付道臣。使之抄出其雹灾所过之里。甚处则以仓谷。白给乾粮。轻处则以还上。计口分给。庶可不至流散矣。 上曰。所达诚是。分付该厅。禀旨举行可也。庚寅进宴后筵中陈戒
庚寅四月。以 上候平复。行进宴。宴讫。臣进前献戒曰。 圣体调摄之馀。宴礼至于日暮。未知 玉候何如。群下尚切忧虑之心矣。 上曰。无事矣。臣曰。今日盛礼。臣僚欢忭之情。何可以言语尽陈也。 圣上未宁之候。累月弥留。而药路未的。群情尤以是煎迫罔措矣。实赖皇天 祖宗默佑之灵应。致有今日之大庆。于此可占 圣算无疆。宝祚绵长。此岂止为一时愆候平复之庆也。 东宫顷日所患之症。在闾阎间。例多弥留。而旋底差安之境。臣民莫不忻幸。今日宴礼仪文。虽曰繁缛。亦何以尽群下抃祝之情也。然小臣之意窃愿 圣上于此益加戒慎。 圣体康宁。而愈谨将摄之节。常若在沈绵之时。邦庆无前。而愈存抑畏之念。常恐失于上天之心。则可以益臻景福。永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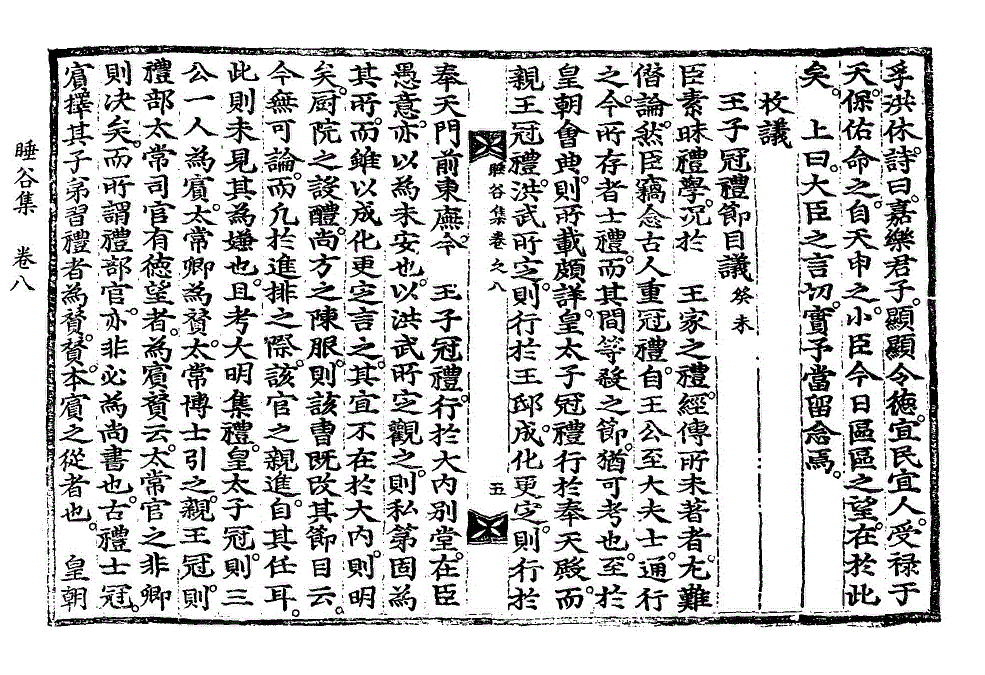 孚洪休。诗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小臣今日区区之望。在于此矣。 上曰。大臣之言切。实予当留念焉。
孚洪休。诗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小臣今日区区之望。在于此矣。 上曰。大臣之言切。实予当留念焉。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收议
王子冠礼节目议(癸未)
臣素昧礼学。况于 王家之礼。经传所未著者。尤难僭论。然臣窃念古人重冠礼。自王公至大夫士。通行之。今所存者士礼。而其间等杀之节。犹可考也。至于皇朝会典。则所载颇详。皇太子冠礼行于奉天殿。而亲王冠礼。洪武所定。则行于王邸。成化更定。则行于奉天门前东庑。今 王子冠礼。行于大内别堂。在臣愚意。亦以为未安也。以洪武所定观之。则私第固为其所。而虽以成化更定言之。其宜不在于大内。则明矣。厨院之设醴。尚方之陈服。则该曹既改其节目云。今无可论。而凡于进排之际。该官之亲进。自其任耳。此则未见其为嫌也。且考大明集礼。皇太子冠。则三公一人为宾。太常卿为赞。太常博士引之。亲王冠。则礼部太常司官有德望者。为宾赞云。太常官之非卿则决矣。而所谓礼部官。亦非必为尚书也。古礼士冠。宾择其子弟习礼者为赞。赞。本宾之从者也。 皇朝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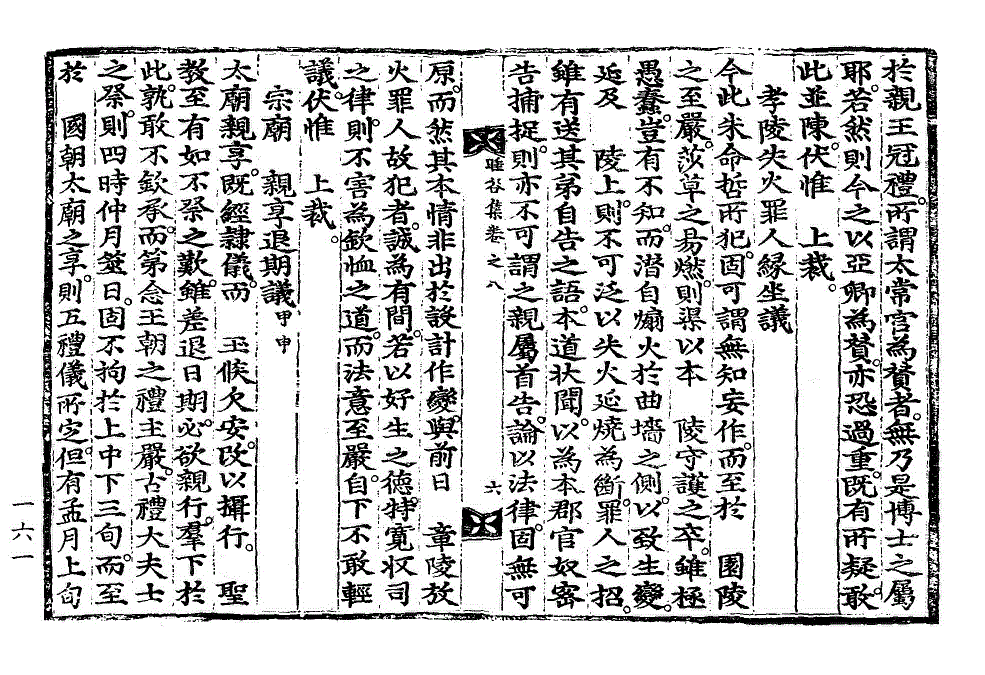 于亲王冠礼。所谓太常官为赞者。无乃是博士之属耶。若然则今之以亚卿为赞。亦恐过重。既有所疑。敢此并陈。伏惟 上裁。
于亲王冠礼。所谓太常官为赞者。无乃是博士之属耶。若然则今之以亚卿为赞。亦恐过重。既有所疑。敢此并陈。伏惟 上裁。孝陵失火罪人缘坐议
今此朱命哲所犯。固可谓无知妄作。而至于 园陵之至严。莎草之易燃。则渠以本 陵守护之卒。虽极愚蠢。岂有不知。而潜自煽火于曲墙之侧。以致生变。延及 陵上。则不可泛以失火延烧为断。罪人之招。虽有送其弟自告之语。本道状闻。以为本郡官奴密告捕捉。则亦不可谓之亲属首告。论以法律。固无可原。而然其本情非出于设计作变。与前日 章陵放火罪人故犯者。诚为有间。若以好生之德。特宽收司之律。则不害为钦恤之道。而法意至严。自下不敢轻议。伏惟 上裁。
宗庙 亲享退期议(甲申)
太庙亲享。既经隶仪。而 玉候欠安。改以摄行。 圣教至有如不祭之叹。虽差退日期。必欲亲行。群下于此。孰敢不钦承。而第念王朝之礼主严。古礼大夫士之祭。则四时仲月筮日。固不拘于上中下三旬。而至于 国朝太庙之享。则五礼仪所定。但有孟月上旬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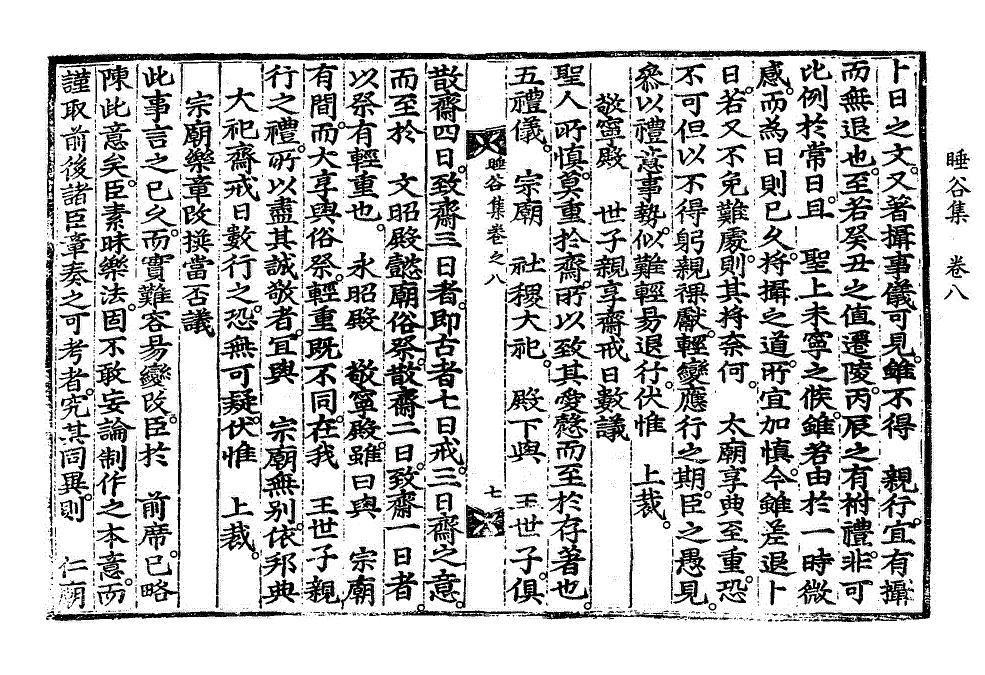 卜日之文。又著摄事仪可见。虽不得 亲行。宜有摄而无退也。至若癸丑之值迁陵。丙辰之有祔礼。非可比例于常日。且 圣上未宁之候。虽若由于一时微感。而为日则已久。将摄之道。所宜加慎。今虽差退卜日。若又不免难处。则其将奈何。 太庙享典至重。恐不可但以不得躬亲祼献。轻变应行之期。臣之愚见。参以礼意事势。似难轻易退行。伏惟 上裁。
卜日之文。又著摄事仪可见。虽不得 亲行。宜有摄而无退也。至若癸丑之值迁陵。丙辰之有祔礼。非可比例于常日。且 圣上未宁之候。虽若由于一时微感。而为日则已久。将摄之道。所宜加慎。今虽差退卜日。若又不免难处。则其将奈何。 太庙享典至重。恐不可但以不得躬亲祼献。轻变应行之期。臣之愚见。参以礼意事势。似难轻易退行。伏惟 上裁。敬宁殿 世子亲享斋戒日数议
圣人所慎。莫重于斋。所以致其爱悫而至于存著也。五礼仪。 宗庙 社稷大祀。 殿下与 王世子。俱散斋四日。致斋三日者。即古者七日戒。三日斋之意。而至于 文昭殿懿庙俗祭。散斋二日。致斋一日者。以祭有轻重也。 永昭殿 敬宁殿。虽曰与 宗庙有间。而大享与俗祭。轻重既不同。在我 王世子亲行之礼。所以尽其诚敬者。宜与 宗庙无别。依邦典 大祀斋戒日数行之。恐无可疑。伏惟 上裁。
宗庙乐章改撰当否议
此事言之已久。而实难容易变改。臣于 前席。已略陈此意矣。臣素昧乐法。固不敢妄论制作之本意。而谨取前后诸臣章奏之可考者。究其同异。则 仁庙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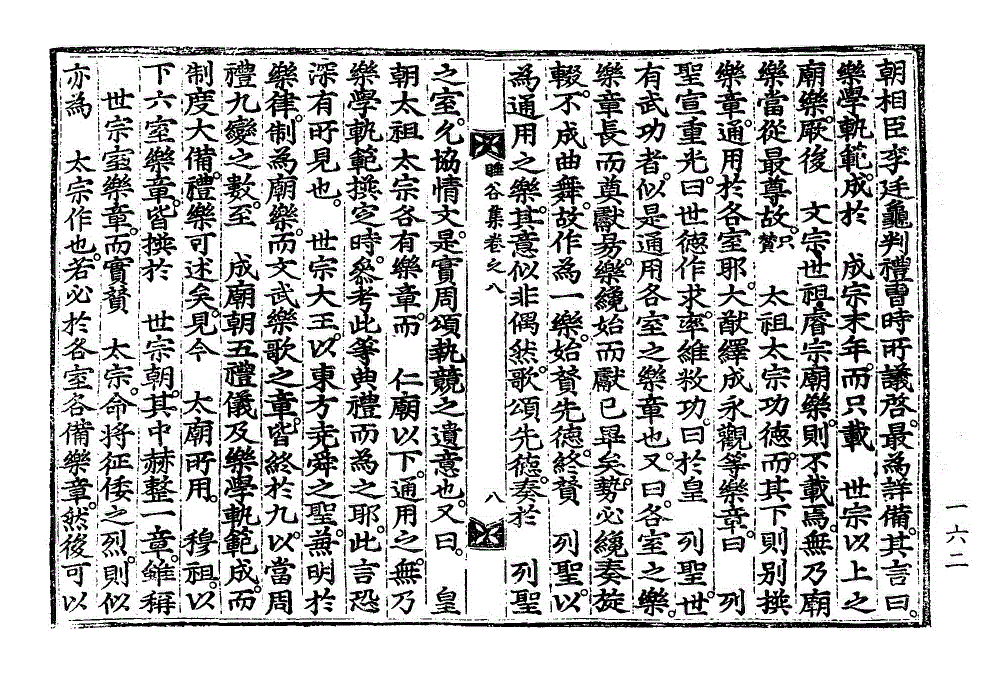 朝相臣李廷龟判礼曹时所议启。最为详备。其言曰。乐学轨范。成于 成宗末年。而只载 世宗以上之庙乐。厥后 文宗,世祖,睿宗庙乐。则不载焉。无乃庙乐当从最尊故。只赞 太祖太宗功德。而其下则别撰乐章。通用于各室耶。大猷绎成永观等乐章。曰 列圣宣重光。曰世德作求。率维敉功。曰于皇 列圣。世有武功者。似是通用各室之乐章也。又曰。各室之乐。乐章长而奠献易。乐才始而献已毕矣。势必才奏旋辍。不成曲舞。故作为一乐。始赞先德。终赞 列圣。以为通用之乐。其意似非偶然。歌颂先德。奏于 列圣之室。允协情文。是实周颂执竞之遗意也。又曰。 皇朝太祖太宗各有乐章。而 仁庙以下。通用之。无乃乐学轨范撰定时。参考此等典礼而为之耶。此言恐深有所见也。 世宗大王。以东方尧舜之圣。兼明于乐律。制为庙乐。而文武乐歌之章。皆终于九。以当周礼九变之数。至 成庙朝五礼仪及乐学轨范成。而制度大备。礼乐可述矣。见今 太庙所用。 穆祖以下六室乐章。皆撰于 世宗朝。其中赫整一章。虽称 世宗室乐章。而实赞 太宗。命将征倭之烈。则似亦为 太宗作也。若必于各室各备乐章。然后可以
朝相臣李廷龟判礼曹时所议启。最为详备。其言曰。乐学轨范。成于 成宗末年。而只载 世宗以上之庙乐。厥后 文宗,世祖,睿宗庙乐。则不载焉。无乃庙乐当从最尊故。只赞 太祖太宗功德。而其下则别撰乐章。通用于各室耶。大猷绎成永观等乐章。曰 列圣宣重光。曰世德作求。率维敉功。曰于皇 列圣。世有武功者。似是通用各室之乐章也。又曰。各室之乐。乐章长而奠献易。乐才始而献已毕矣。势必才奏旋辍。不成曲舞。故作为一乐。始赞先德。终赞 列圣。以为通用之乐。其意似非偶然。歌颂先德。奏于 列圣之室。允协情文。是实周颂执竞之遗意也。又曰。 皇朝太祖太宗各有乐章。而 仁庙以下。通用之。无乃乐学轨范撰定时。参考此等典礼而为之耶。此言恐深有所见也。 世宗大王。以东方尧舜之圣。兼明于乐律。制为庙乐。而文武乐歌之章。皆终于九。以当周礼九变之数。至 成庙朝五礼仪及乐学轨范成。而制度大备。礼乐可述矣。见今 太庙所用。 穆祖以下六室乐章。皆撰于 世宗朝。其中赫整一章。虽称 世宗室乐章。而实赞 太宗。命将征倭之烈。则似亦为 太宗作也。若必于各室各备乐章。然后可以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3H 页
 格思。则 世宗,文宗,世祖,睿宗四室乐章。宜备于 成庙之世。而轨范无著焉。此必非放过而然也。顾以 成庙之所未撰。而追撰于后。岂所可易言哉。惟 宣庙室重光章。追撰于 仁庙朝。而以补初献乐章字句不足之数。乐则无变。然臣犹未知其九章之外。添入一章。能无失于九变之义否也。至于尽废旧乐章。就十一室。各撰一章。或别撰通用之九章。则事体至重。非臣謏寡之见所可议其当否。伏惟 上裁。
格思。则 世宗,文宗,世祖,睿宗四室乐章。宜备于 成庙之世。而轨范无著焉。此必非放过而然也。顾以 成庙之所未撰。而追撰于后。岂所可易言哉。惟 宣庙室重光章。追撰于 仁庙朝。而以补初献乐章字句不足之数。乐则无变。然臣犹未知其九章之外。添入一章。能无失于九变之义否也。至于尽废旧乐章。就十一室。各撰一章。或别撰通用之九章。则事体至重。非臣謏寡之见所可议其当否。伏惟 上裁。雅乐舞佾人数复旧用八当否议
臣更详五礼仪。 社稷,风云雷雨,先农,先蚕,雩祀,文宣王。则祭用雅乐。而舞六佾。每佾八人。 宗庙,永宁殿,文昭殿,懿庙。则祭用俗乐。而舞六佾。每佾六人。其为六佾则同。而人数多寡。有雅俗乐之异矣。舞佾之法。天子八诸侯六。而每佾人数如其佾数。或曰。每佾八人。朱子并存两说于论语集注。而谓未详孰是。以此观之。其隆杀之节。系于佾数。似不系于人数也。 社稷以下用雅乐处。所为祭之神。宜用八佾。而止于六佾者。以祀在藩邦也。然其人数之用八。与俗乐异者。尚亦有隆杀之意而然欤。臣见识寡陋。难容臆说于其间也。且臣追闻礼官之言。则诸处祀享时日各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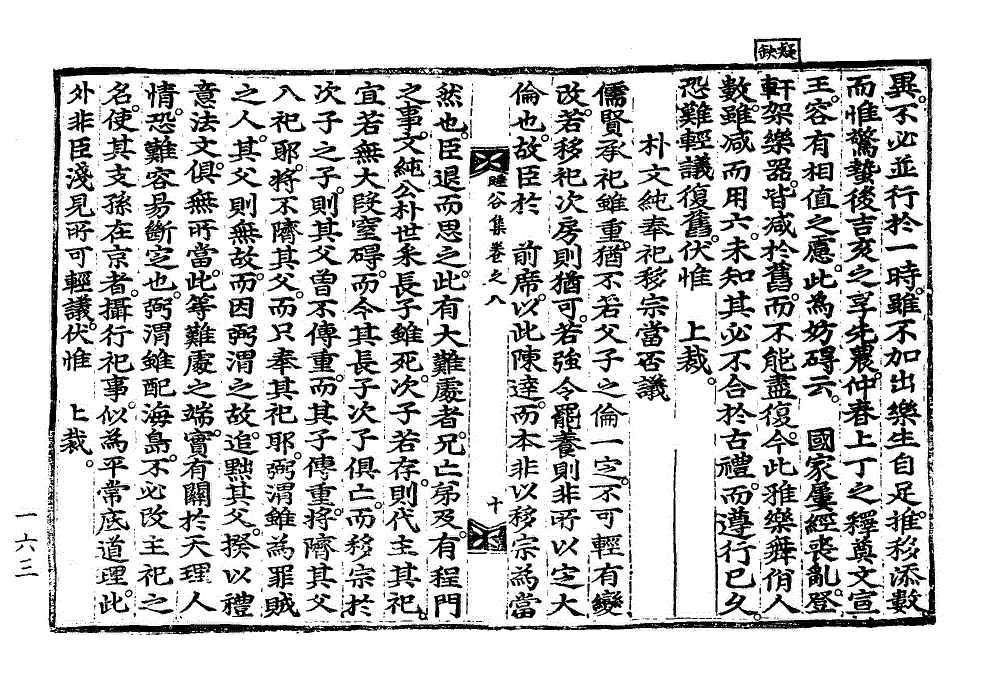 异。不必并行于一时。虽不加出乐生自足。推移添数。而惟惊蛰后吉亥之享先农。仲春上丁之释奠文宣王。容有相值之虑。此为妨碍云。 国家屡经丧乱。登轩架乐器。皆减于旧。而不能尽复。今此雅乐舞佾人数。虽减而用六。未知其必不合于古礼。而遵行已久。恐难轻议复旧。伏惟 上裁。주-D001
异。不必并行于一时。虽不加出乐生自足。推移添数。而惟惊蛰后吉亥之享先农。仲春上丁之释奠文宣王。容有相值之虑。此为妨碍云。 国家屡经丧乱。登轩架乐器。皆减于旧。而不能尽复。今此雅乐舞佾人数。虽减而用六。未知其必不合于古礼。而遵行已久。恐难轻议复旧。伏惟 上裁。주-D001朴文纯奉祀移宗当否议
儒贤承祀虽重。犹不若父子之伦一定。不可轻有变改。若移祀次房则犹可。若强令罢养则非所以定大伦也。故臣于 前席。以此陈达。而本非以移宗为当然也。臣退而思之。此有大难处者。兄亡弟及。有程门之事。文纯公朴世采长子虽死。次子若存。则代主其祀。宜若无大段窒碍。而今其长子次子俱亡。而移宗于次子之子。则其父曾不传重。而其子传重。将隮其父入祀耶。将不隮其父。而只奉其祀耶。弼渭虽为罪贼之人。其父则无故。而因弼渭之故。追黜其父。揆以礼意法文。俱无所当。此等难处之端。实有关于天理人情。恐难容易断定也。弼渭虽配海岛。不必改主祀之名。使其支孙在京者。摄行祀事。似为平常底道理。此外非臣浅见所可轻议。伏惟 上裁。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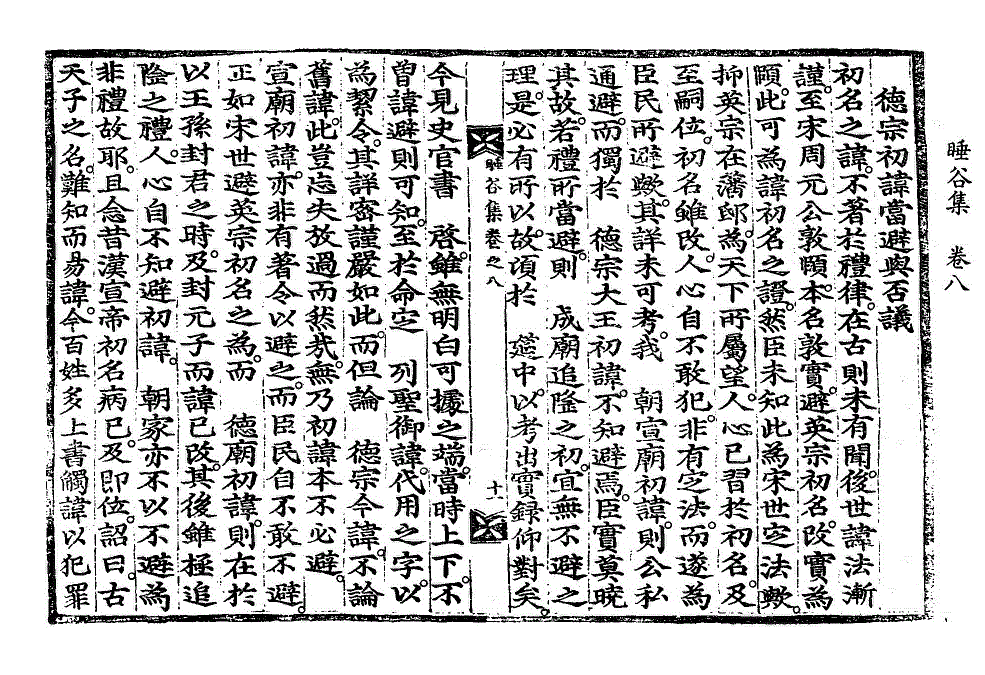 德宗初讳当避与否议
德宗初讳当避与否议初名之讳。不著于礼律。在古则未有闻。后世讳法渐谨。至宋周元公敦颐。本名敦实。避英宗初名。改实为颐。此可为讳初名之證。然臣未知此为宋世定法欤。抑英宗在藩邸。为天下所属望。人心已习于初名。及至嗣位。初名虽改。人心自不敢犯。非有定法。而遂为臣民所避欤。其详未可考。我 朝宣庙初讳。则公私通避。而独于 德宗大王初讳。不知避焉。臣实莫晓其故。若礼所当避。则 成庙追隆之初。宜无不避之理。是必有所以。故顷于 筵中。以考出实录仰对矣。今见史官书 启。虽无明白可据之端。当时上下。不曾讳避则可知。至于命定 列圣御讳。代用之字。以为絜令。其详密谨严如此。而但论 德宗今讳。不论旧讳。此岂忘失放过而然哉。无乃初讳本不必避。 宣庙初讳。亦非有著令以避之。而臣民自不敢不避。正如宋世避英宗初名之为。而 德庙初讳。则在于以王孙封君之时。及封元子而讳已改。其后虽极追隆之礼。人心自不知避初讳。 朝家亦不以不避为非礼故耶。且念昔汉宣帝初名病已。及即位。诏曰。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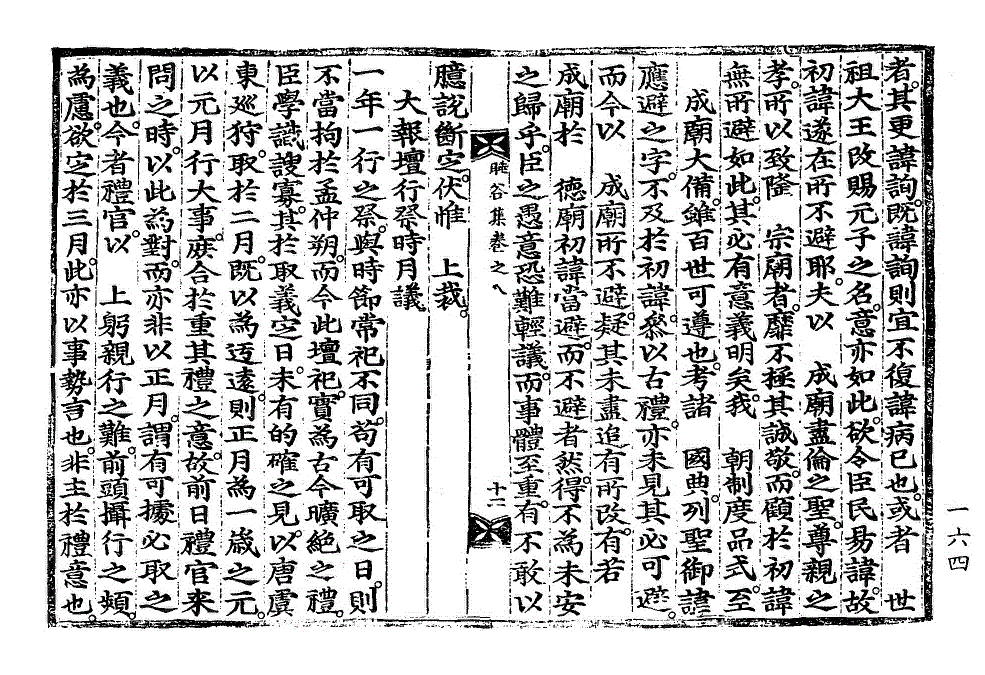 者。其更讳询。既讳询则宜不复讳病已也。或者 世祖大王改赐元子之名。意亦如此。欲令臣民易讳。故初讳遂在所不避耶。夫以 成庙尽伦之圣。尊亲之孝。所以致隆 宗庙者。靡不极其诚敬。而顾于初讳无所避如此。其必有意义明矣。我 朝制度品式。至 成庙大备。虽百世可遵也。考诸 国典。列圣御讳应避之字。不及于初讳。参以古礼。亦未见其必可避。而今以 成庙所不避。疑其未尽追有所改。有若 成庙于 德庙初讳当避。而不避者然。得不为未安之归乎。臣之愚意恐难轻议。而事体至重。有不敢以臆说断定。伏惟 上裁。
者。其更讳询。既讳询则宜不复讳病已也。或者 世祖大王改赐元子之名。意亦如此。欲令臣民易讳。故初讳遂在所不避耶。夫以 成庙尽伦之圣。尊亲之孝。所以致隆 宗庙者。靡不极其诚敬。而顾于初讳无所避如此。其必有意义明矣。我 朝制度品式。至 成庙大备。虽百世可遵也。考诸 国典。列圣御讳应避之字。不及于初讳。参以古礼。亦未见其必可避。而今以 成庙所不避。疑其未尽追有所改。有若 成庙于 德庙初讳当避。而不避者然。得不为未安之归乎。臣之愚意恐难轻议。而事体至重。有不敢以臆说断定。伏惟 上裁。大报坛行祭时月议
一年一行之祭。与时节常祀不同。苟有可取之日。则不当拘于孟仲朔。而今此坛祀。实为古今旷绝之礼。臣学识謏寡。其于取义定日。未有的确之见。以唐虞东巡狩。取于二月。既以为迂远。则正月为一岁之元。以元月行大事。庶合于重其礼之意。故前日礼官来问之时。以此为对。而亦非以正月。谓有可据必取之义也。今者礼官。以 上躬亲行之难。前头摄行之频。为虑。欲定于三月。此亦以事势言也。非主于礼意也。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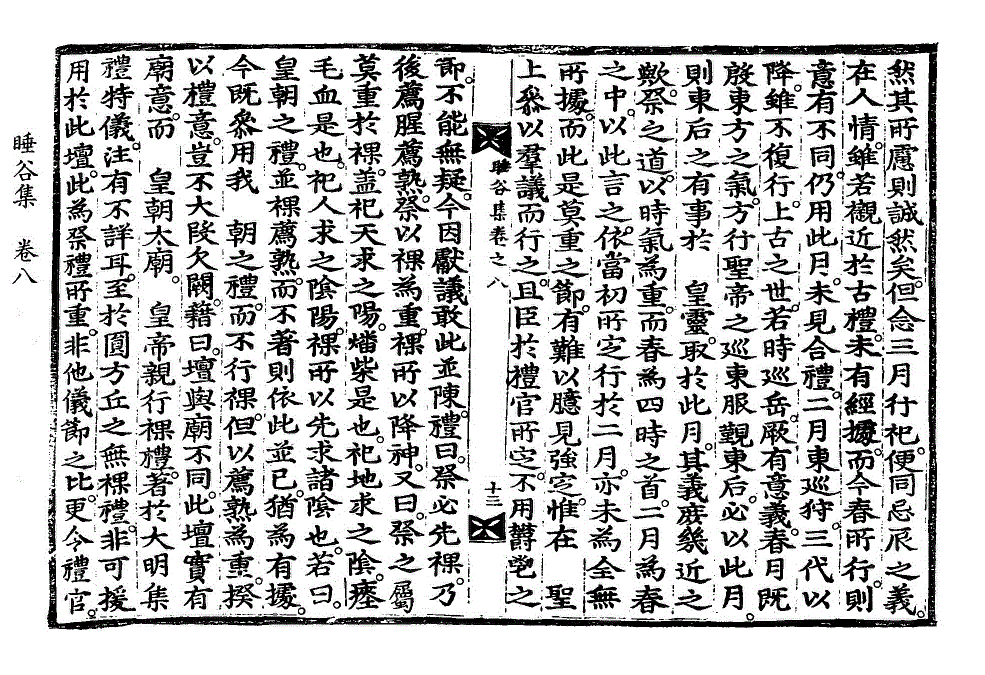 然其所虑则诚然矣。但念三月行祀。便同忌辰之义。在人情。虽若衬近于古礼。未有经据。而今春所行。则意有不同。仍用此月。未见合礼。二月东巡狩。三代以降。虽不复行。上古之世。若时巡岳。厥有意义。春月既殷东方之气。方行圣帝之巡东服觐东后。必以此月。则东后之有事于 皇灵。取于此月。其义庶几近之欤。祭之道。以时气为重。而春为四时之首。二月为春之中。以此言之。依当初所定行于二月。亦未为全无所据。而此是莫重之节。有难以臆见强定。惟在 圣上参以群议而行之。且臣于礼官所定。不用郁鬯之节。不能无疑。今因献议敢此并陈。礼曰。祭必先祼。乃后荐腥荐熟。祭以祼为重。祼所以降神。又曰。祭之属莫重于祼。盖祀天求之阳。燔柴是也。祀地求之阴。瘗毛血是也。祀人求之阴阳。祼所以先求诸阴也。若曰。皇朝之礼。并祼荐熟。而不著则依此并已。犹为有据。今既参用我 朝之礼。而不行祼。但以荐熟为重。揆以礼意。岂不大段欠阙。藉曰。坛与庙不同。此坛实有庙意。而 皇朝太庙。 皇帝亲行祼礼。著于大明集礼特仪。注有不详耳。至于圆方丘之无祼礼。非可援用于此坛。此为祭礼所重。非他仪节之比。更令礼官。
然其所虑则诚然矣。但念三月行祀。便同忌辰之义。在人情。虽若衬近于古礼。未有经据。而今春所行。则意有不同。仍用此月。未见合礼。二月东巡狩。三代以降。虽不复行。上古之世。若时巡岳。厥有意义。春月既殷东方之气。方行圣帝之巡东服觐东后。必以此月。则东后之有事于 皇灵。取于此月。其义庶几近之欤。祭之道。以时气为重。而春为四时之首。二月为春之中。以此言之。依当初所定行于二月。亦未为全无所据。而此是莫重之节。有难以臆见强定。惟在 圣上参以群议而行之。且臣于礼官所定。不用郁鬯之节。不能无疑。今因献议敢此并陈。礼曰。祭必先祼。乃后荐腥荐熟。祭以祼为重。祼所以降神。又曰。祭之属莫重于祼。盖祀天求之阳。燔柴是也。祀地求之阴。瘗毛血是也。祀人求之阴阳。祼所以先求诸阴也。若曰。皇朝之礼。并祼荐熟。而不著则依此并已。犹为有据。今既参用我 朝之礼。而不行祼。但以荐熟为重。揆以礼意。岂不大段欠阙。藉曰。坛与庙不同。此坛实有庙意。而 皇朝太庙。 皇帝亲行祼礼。著于大明集礼特仪。注有不详耳。至于圆方丘之无祼礼。非可援用于此坛。此为祭礼所重。非他仪节之比。更令礼官。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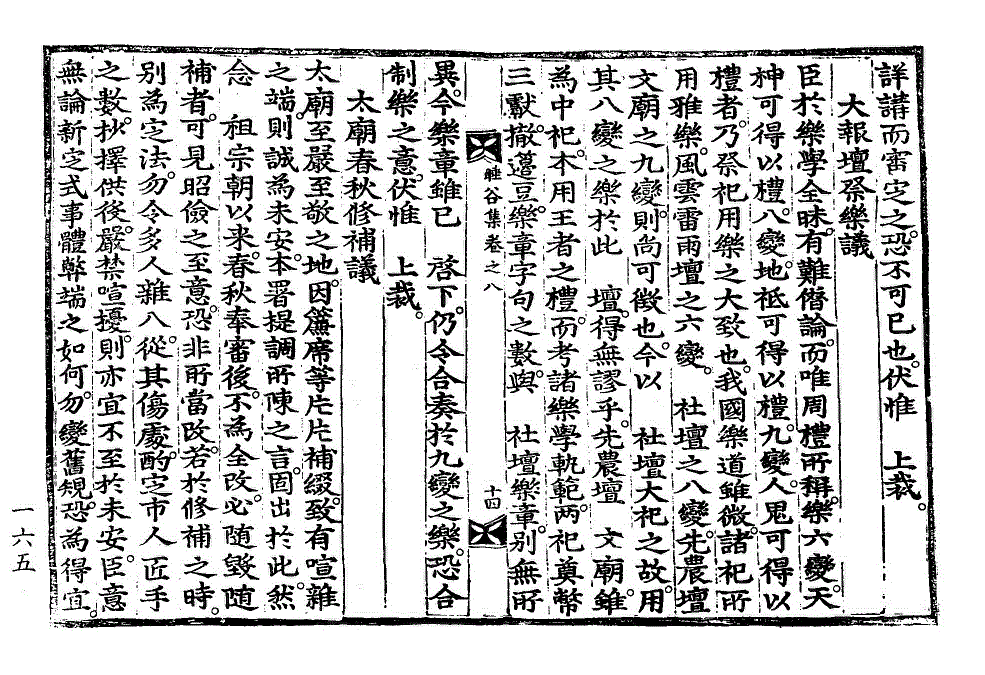 详讲而审定之。恐不可已也。伏惟 上裁。
详讲而审定之。恐不可已也。伏惟 上裁。大报坛祭乐议
臣于乐学全昧。有难僭论。而唯周礼所称。乐六变。天神可得以礼。八变。地祗可得以礼。九变。人鬼可得以礼者。乃祭祀用乐之大致也。我国乐道虽微。诸祀所用雅乐。风云雷雨坛之六变。 社坛之八变。先农坛文庙之九变。则尚可徵也。今以 社坛大祀之故。用其八变之乐于此 坛。得无谬乎。先农坛 文庙。虽为中祀。本用王者之礼。而考诸乐学轨范。两祀奠币三献。撤笾豆。乐章字句之数。与 社坛乐章。别无所异。今乐章虽已 启下。仍令合奏于九变之乐。恐合制乐之意。伏惟 上裁。
太庙春秋修补议
太庙至严至敬之地。因帘席等片片补缀。致有喧杂之端。则诚为未安。本署提调所陈之言。固出于此。然念 祖宗朝以来。春秋奉审后。不为全改。必随毁随补者。可见昭俭之至意。恐非所当改。若于修补之时。别为定法。勿令多人杂入。从其伤处。酌定市人匠手之数。抄择供役。严禁喧扰。则亦宜不至于未安。臣意无论新定式事体弊端之如何。勿变旧规。恐为得宜。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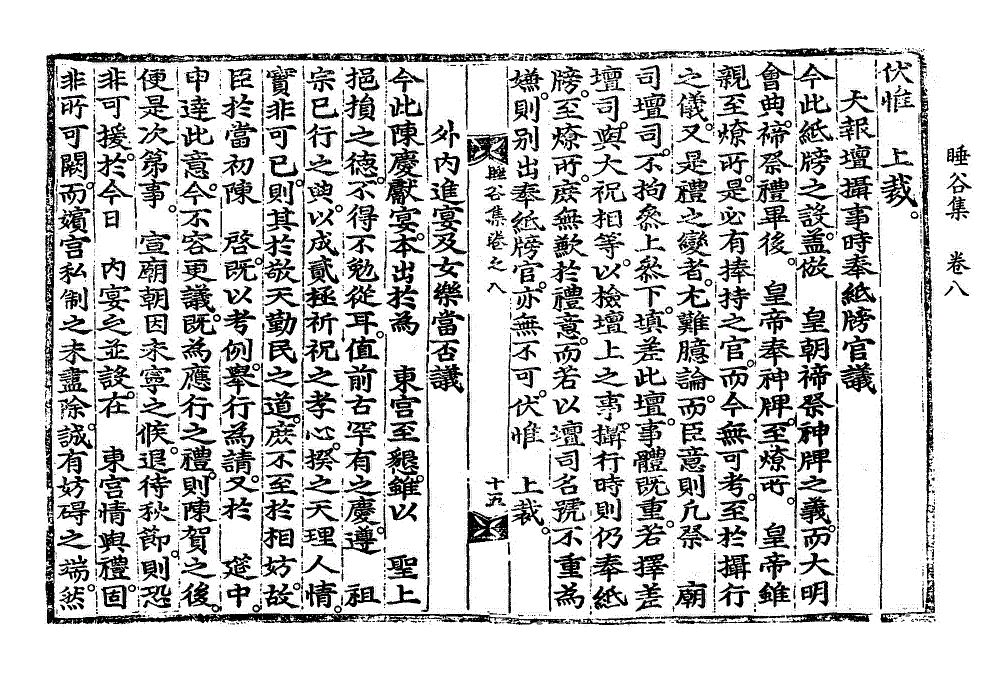 伏惟 上裁。
伏惟 上裁。大报坛摄事时奉纸榜官议
今此纸榜之设。盖仿 皇朝禘祭神牌之义。而大明会典。禘祭礼毕后。 皇帝奉神牌。至燎所。 皇帝虽亲至燎所。是必有捧持之官。而今无可考。至于摄行之仪。又是礼之变者。尤难臆论。而臣意则凡祭 庙司坛司。不拘参上参下。填差此坛。事体既重。若择差坛司。与大祝相等。以检坛上之事。摄行时则仍奉纸榜。至燎所。庶无歉于礼意。而若以坛司名号不重为嫌。则别出奉纸榜官。亦无不可。伏惟 上裁。
外内进宴及女乐当否议
今此陈庆献宴。本出于为 东宫至恳。虽以 圣上挹损之德。不得不勉从耳。值前古罕有之庆。遵 祖宗已行之典。以成贰极祈祝之孝心。揆之天理人情。实非可已。则其于敬天勤民之道。庶不至于相妨。故臣于当初陈 启。既以考例。举行为请。又于 筵中。申达此意。今不容更议。既为应行之礼。则陈贺之后。便是次第事。 宣庙朝因未宁之候。退待秋节。则恐非可援。于今日 内宴之并设。在 东宫情与礼。固非所可阙。而嫔宫私制之未尽除。诚有妨碍之端。然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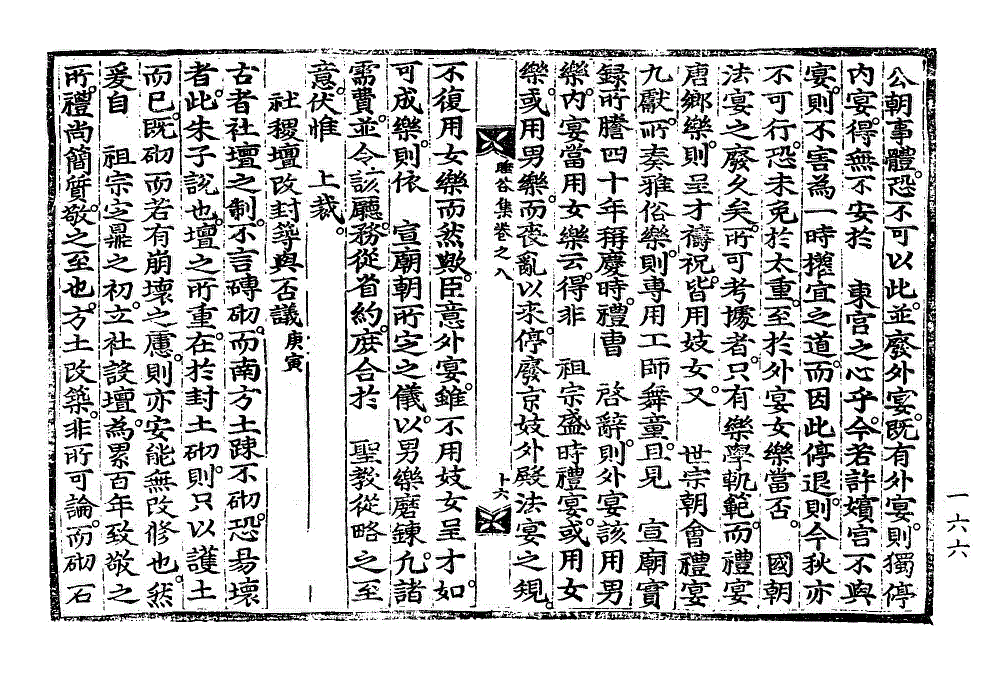 公朝事体。恐不可以此。并废外宴。既有外宴。则独停内宴。得无不安于 东宫之心乎。今若许嫔宫不与宴。则不害为一时权宜之道。而因此停退。则今秋亦不可行。恐未免于太重。至于外宴女乐当否。 国朝法宴之废久矣。所可考据者。只有乐学轨范。而礼宴唐乡乐。则呈才祷祝。皆用妓女。又 世宗朝会礼宴九献。所奏雅俗乐。则专用工师舞童。且见 宣庙实录所誊四十年称庆时。礼曹 启辞。则外宴该用男乐。内宴当用女乐云。得非 祖宗盛时礼宴。或用女乐。或用男乐。而丧乱以来。停废京妓外殿法宴之规。不复用女乐而然欤。臣意外宴。虽不用妓女呈才。如可成乐。则依 宣庙朝所定之仪。以男乐磨鍊。凡诸需费。并令该厅。务从省约。庶合于 圣教从略之至意。伏惟 上裁。
公朝事体。恐不可以此。并废外宴。既有外宴。则独停内宴。得无不安于 东宫之心乎。今若许嫔宫不与宴。则不害为一时权宜之道。而因此停退。则今秋亦不可行。恐未免于太重。至于外宴女乐当否。 国朝法宴之废久矣。所可考据者。只有乐学轨范。而礼宴唐乡乐。则呈才祷祝。皆用妓女。又 世宗朝会礼宴九献。所奏雅俗乐。则专用工师舞童。且见 宣庙实录所誊四十年称庆时。礼曹 启辞。则外宴该用男乐。内宴当用女乐云。得非 祖宗盛时礼宴。或用女乐。或用男乐。而丧乱以来。停废京妓外殿法宴之规。不复用女乐而然欤。臣意外宴。虽不用妓女呈才。如可成乐。则依 宣庙朝所定之仪。以男乐磨鍊。凡诸需费。并令该厅。务从省约。庶合于 圣教从略之至意。伏惟 上裁。社稷坛改封筑与否议(庚寅)
古者社坛之制。不言砖砌。而南方土疏不砌。恐易坏者。此朱子说也。坛之所重。在于封土砌。则只以护土而已。既砌而若有崩坏之虑。则亦安能无改修也。然爰自 祖宗定鼎之初。立社设坛。为累百年致敬之所。礼尚简质。敬之至也。方土改筑。非所可论。而砌石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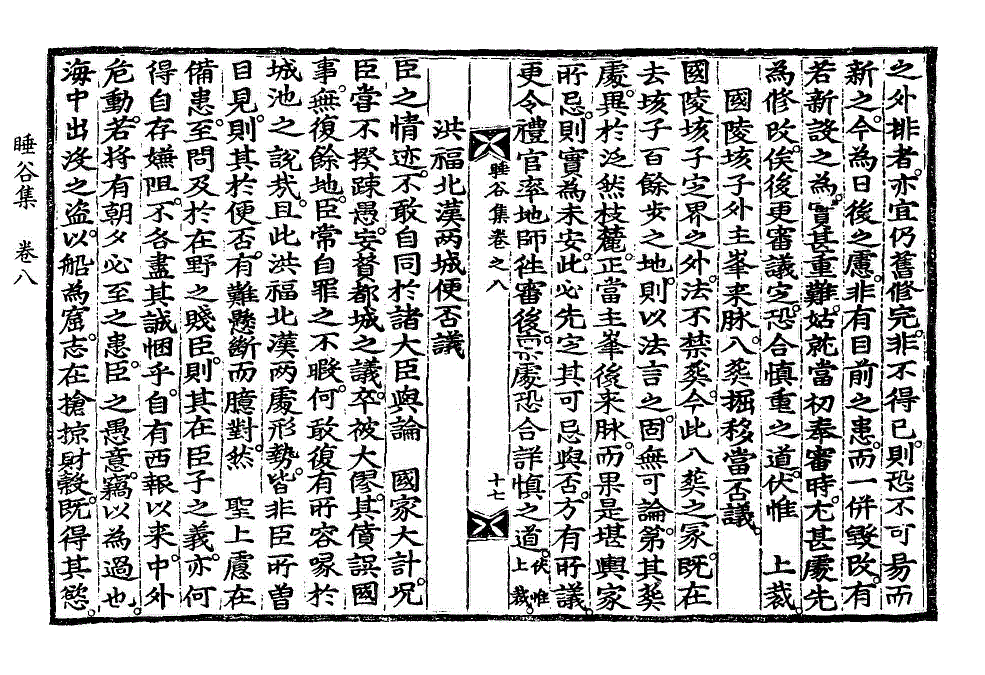 之外排者。亦宜仍旧修完。非不得已。则恐不可易而新之。今为日后之虑。非有目前之患。而一并毁改。有若新设之为。实甚重难。姑就当初奉审时。尤甚处先为修改。俟后更审议定。恐合慎重之道。伏惟 上裁。
之外排者。亦宜仍旧修完。非不得已。则恐不可易而新之。今为日后之虑。非有目前之患。而一并毁改。有若新设之为。实甚重难。姑就当初奉审时。尤甚处先为修改。俟后更审议定。恐合慎重之道。伏惟 上裁。国陵垓子外主峰来脉。入葬掘移当否议
国陵垓子定界之外。法不禁葬。今此入葬之冢。既在去垓子百馀步之地。则以法言之。固无可论。第其葬处。异于泛然枝麓。正当主峰后来脉。而果是堪舆家所忌。则实为未安。此必先定其可忌与否。方有所议。更令礼官率地师往审后。禀处恐合详慎之道。伏惟上裁。
洪福,北汉两城便否议
臣之情迹。不敢自同于诸大臣与论 国家大计。况臣尝不揆疏愚。妄赞都城之议。卒被大僇。其偾误国事。无复馀地。臣常自罪之不暇。何敢复有所容喙于城池之说哉。且此洪福,北汉两处形势。皆非臣所曾目见。则其于便否。有难悬断而臆对。然 圣上虑在备患。至问及于在野之贱臣。则其在臣子之义。亦何得自存嫌阻。不各尽其诚悃乎。自有西报以来。中外危动。若将有朝夕必至之患。臣之愚意。窃以为过也。海中出没之盗。以船为窟。志在抢掠财谷。既得其欲。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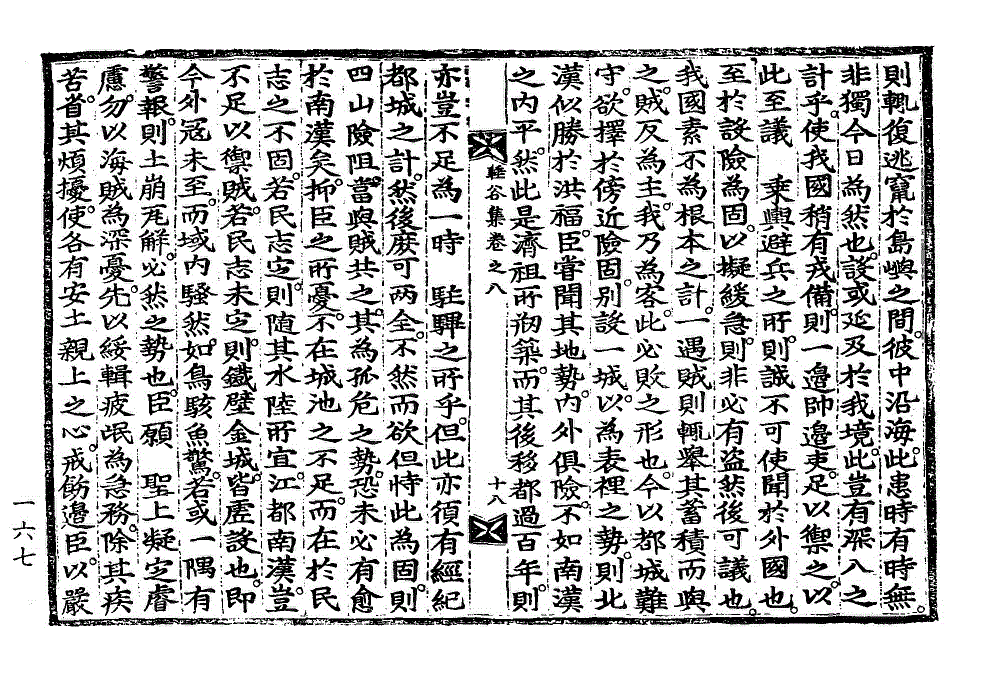 则辄复逃窜于岛屿之间。彼中沿海。此患时有时无。非独今日为然也。设或延及于我境。此岂有深入之计乎。使我国稍有戎备。则一边帅边吏。足以御之。以此至议 乘舆避兵之所。则诚不可使闻于外国也。至于设险为固。以拟缓急。则非必有盗然后可议也。我国素不为根本之计。一遇贼则辄举其蓄积而与之。贼反为主。我乃为客。此必败之形也。今以都城难守。欲择于傍近险固。别设一城。以为表里之势。则北汉似胜于洪福。臣尝闻其地势。内外俱险。不如南汉之内平。然此是济祖所刱筑。而其后移都过百年。则亦岂不足为一时 驻跸之所乎。但此亦须有经纪都城之计。然后庶可两全。不然而欲但恃此为固。则四山险阻。当与贼共之。其为孤危之势。恐未必有愈于南汉矣。抑臣之所忧。不在城池之不足。而在于民志之不固。若民志定。则随其水陆所宜。江都,南汉。岂不足以御贼。若民志未定。则铁壁金城。皆虚设也。即今外寇未至。而域内骚然。如鸟骇鱼惊。若或一隅有警报。则土崩瓦解。必然之势也。臣愿 圣上凝定睿虑。勿以海贼为深忧。先以绥辑疲氓为急务。除其疾苦。省其烦扰。使各有安土亲上之心。戒饬边臣。以严
则辄复逃窜于岛屿之间。彼中沿海。此患时有时无。非独今日为然也。设或延及于我境。此岂有深入之计乎。使我国稍有戎备。则一边帅边吏。足以御之。以此至议 乘舆避兵之所。则诚不可使闻于外国也。至于设险为固。以拟缓急。则非必有盗然后可议也。我国素不为根本之计。一遇贼则辄举其蓄积而与之。贼反为主。我乃为客。此必败之形也。今以都城难守。欲择于傍近险固。别设一城。以为表里之势。则北汉似胜于洪福。臣尝闻其地势。内外俱险。不如南汉之内平。然此是济祖所刱筑。而其后移都过百年。则亦岂不足为一时 驻跸之所乎。但此亦须有经纪都城之计。然后庶可两全。不然而欲但恃此为固。则四山险阻。当与贼共之。其为孤危之势。恐未必有愈于南汉矣。抑臣之所忧。不在城池之不足。而在于民志之不固。若民志定。则随其水陆所宜。江都,南汉。岂不足以御贼。若民志未定。则铁壁金城。皆虚设也。即今外寇未至。而域内骚然。如鸟骇鱼惊。若或一隅有警报。则土崩瓦解。必然之势也。臣愿 圣上凝定睿虑。勿以海贼为深忧。先以绥辑疲氓为急务。除其疾苦。省其烦扰。使各有安土亲上之心。戒饬边臣。以严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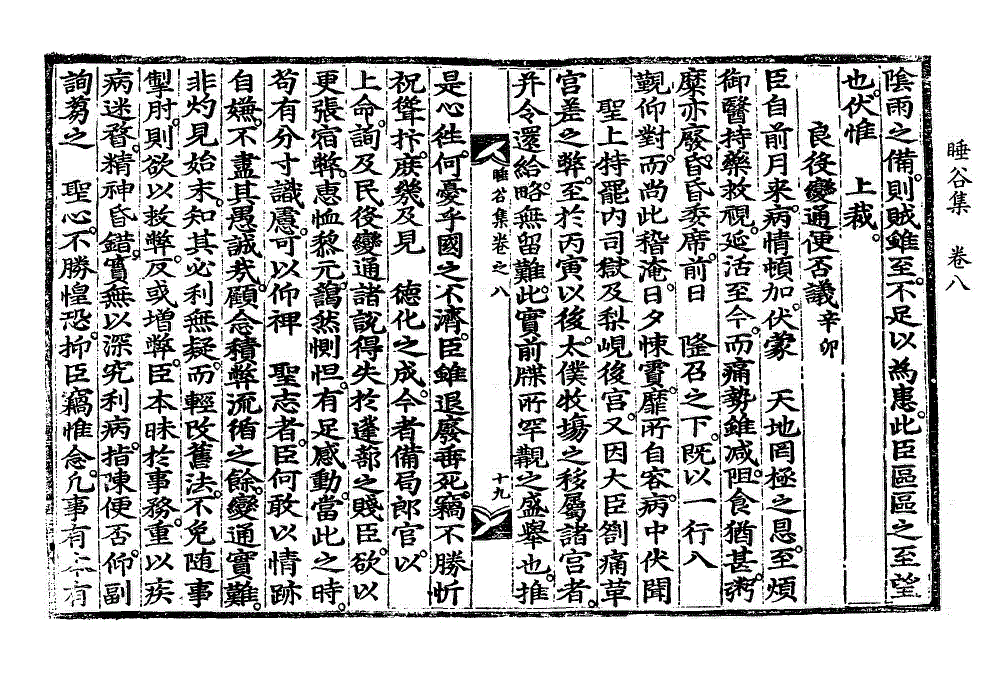 阴雨之备。则贼虽至。不足以为患。此臣区区之至望也。伏惟 上裁。
阴雨之备。则贼虽至。不足以为患。此臣区区之至望也。伏惟 上裁。良役变通便否议(辛卯)
臣自前月来。病情顿加。伏蒙 天地罔极之恩。至烦御医持药救视。延活至今。而痛势虽减。阻食犹甚。粥糜亦废。昏昏委席。前日 隆召之下。既以一行入 觐仰对。而尚此稽淹。日夕悚霣。靡所自容。病中伏闻 圣上特罢内司狱及梨岘后宫。又因大臣劄痛革宫差之弊。至于丙寅以后。太仆牧场之移属诸宫者。并令还给。略无留难。此实前牒所罕觏之盛举也。推是心往。何忧乎国之不济。臣虽退废垂死。窃不胜忻祝耸抃。庶几及见 德化之成。今者备局郎官。以 上命。询及民役变通诸说得失于蓬蔀之贱臣。欲以更张宿弊。惠恤黎元。蔼然恻怛。有足感动。当此之时。苟有分寸识虑。可以仰裨 圣志者。臣何敢以情迹自嫌。不尽其愚诚哉。顾念积弊流循之馀。变通实难。非灼见始末。知其必利无疑。而轻改旧法。不免随事掣肘。则欲以救弊。反或增弊。臣本昧于事务。重以疾病迷瞀。精神昏错。实无以深究利病。指陈便否。仰副询刍之 圣心。不胜惶恐。抑臣窃惟念。凡事有本有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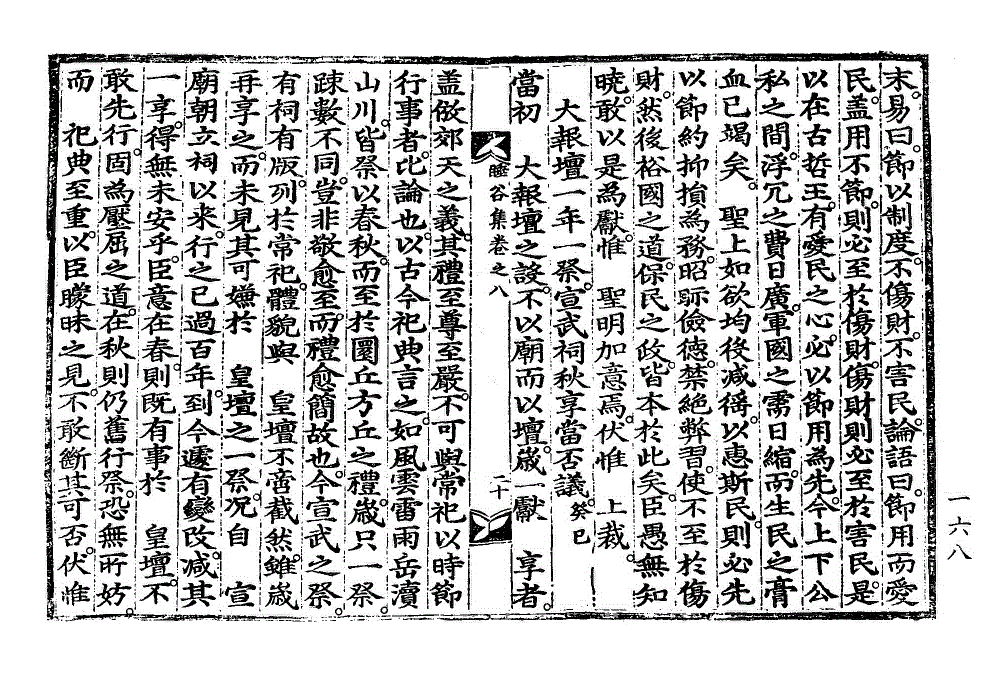 末。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论语曰。节用而爱民。盖用不节。则必至于伤财。伤财则必至于害民。是以在古哲王。有爱民之心。必以节用为先。今上下公私之间。浮冗之费日广。军国之需日缩。而生民之膏血已竭矣。 圣上如欲均役减徭。以惠斯民。则必先以节约抑损为务。昭视俭德。禁绝弊习。使不至于伤财。然后裕国之道。保民之政。皆本于此矣。臣愚无知晓。敢以是为献。惟 圣明加意焉。伏惟 上裁。
末。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论语曰。节用而爱民。盖用不节。则必至于伤财。伤财则必至于害民。是以在古哲王。有爱民之心。必以节用为先。今上下公私之间。浮冗之费日广。军国之需日缩。而生民之膏血已竭矣。 圣上如欲均役减徭。以惠斯民。则必先以节约抑损为务。昭视俭德。禁绝弊习。使不至于伤财。然后裕国之道。保民之政。皆本于此矣。臣愚无知晓。敢以是为献。惟 圣明加意焉。伏惟 上裁。大报坛一年一祭。宣武祠秋享当否议。(癸巳)
当初 大报坛之设。不以庙而以坛。岁一献 享者。盖仿郊天之义。其礼至尊至严。不可与常祀以时节行事者。比论也。以古今祀典言之。如风云雷雨岳渎山川。皆祭以春秋。而至于圜丘方丘之礼。岁只一祭。疏数不同。岂非敬愈至。而礼愈简故也。今宣武之祭。有祠有版。列于常祀。体貌与 皇坛不啻截然。虽岁再享之。而未见其可嫌于 皇坛之一祭。况自 宣庙朝立祠以来。行之已过百年。到今遽有变改。减其一享。得无未安乎。臣意在春。则既有事于 皇坛。不敢先行。固为压屈之道。在秋则仍旧行祭。恐无所妨。而 祀典至重。以臣矇昧之见。不敢断其可否。伏惟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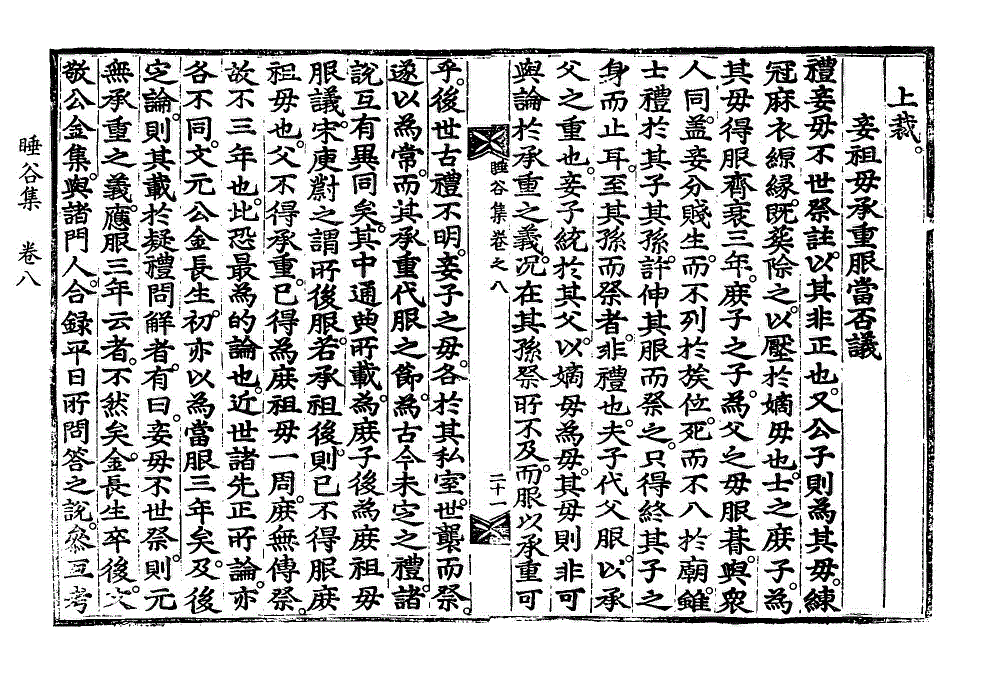 上裁。
上裁。妾祖母承重服当否议
礼妾母不世祭注。以其非正也。又公子则为其母。练冠麻衣縓缘。既葬除之。以压于嫡母也。士之庶子。为其母得服齐衰三年。庶子之子。为父之母服期。与众人同。盖妾分贱生。而不列于族位。死而不入于庙。虽士礼于其子其孙。许伸其服而祭之。只得终其子之身而止耳。至其孙而祭者。非礼也。夫子代父服。以承父之重也。妾子统于其父。以嫡母为母。其母则非可与论于承重之义。况在其孙祭所不及。而服以承重可乎。后世古礼不明。妾子之母。各于其私室。世袭而祭。遂以为常。而其承重代服之节。为古今未定之礼。诸说互有异同矣。其中通典所载。为庶子后为庶祖母服议。宋庾蔚之谓所后服。若承祖后。则己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得承重。己得为庶祖母一周。庶无传祭。故不三年也。此恐最为的论也。近世诸先正所论。亦各不同。文元公金长生。初亦以为当服三年矣。及后定论。则其载于疑礼问解者。有曰。妾母不世祭。则元无承重之义。应服三年云者。不然矣。金长生卒后。文敬公金集。与诸门人。合录平日所问答之说。参互考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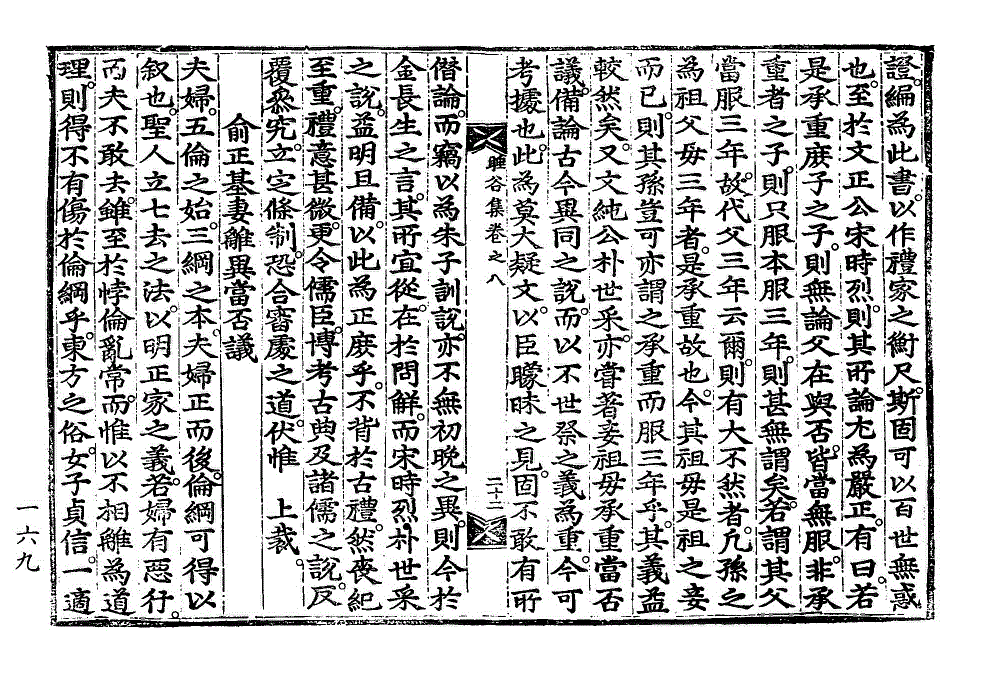 證。编为此书。以作礼家之衡尺。斯固可以百世无惑也。至于文正公宋时烈。则其所论尤为严正。有曰。若是承重庶子之子。则无论父在与否。皆当无服。非承重者之子。则只服本服三年。则甚无谓矣。若谓其父当服三年。故代父三年云尔。则有大不然者。凡孙之为祖父母三年者。是承重故也。今其祖母是祖之妾而已。则其孙岂可亦谓之承重而服三年乎。其义益较然矣。又文纯公朴世采。亦尝著妾祖母承重当否议。备论古今异同之说。而以不世祭之义为重。今可考据也。此为莫大疑文。以臣矇昧之见。固不敢有所僭论。而窃以为朱子训说。亦不无初晚之异。则今于金长生之言。其所宜从。在于问解。而宋时烈,朴世采之说。益明且备。以此为正庶乎。不背于古礼。然丧纪至重。礼意甚微。更令儒臣。博考古典及诸儒之说。反覆参究。立定条制。恐合审处之道。伏惟 上裁。
證。编为此书。以作礼家之衡尺。斯固可以百世无惑也。至于文正公宋时烈。则其所论尤为严正。有曰。若是承重庶子之子。则无论父在与否。皆当无服。非承重者之子。则只服本服三年。则甚无谓矣。若谓其父当服三年。故代父三年云尔。则有大不然者。凡孙之为祖父母三年者。是承重故也。今其祖母是祖之妾而已。则其孙岂可亦谓之承重而服三年乎。其义益较然矣。又文纯公朴世采。亦尝著妾祖母承重当否议。备论古今异同之说。而以不世祭之义为重。今可考据也。此为莫大疑文。以臣矇昧之见。固不敢有所僭论。而窃以为朱子训说。亦不无初晚之异。则今于金长生之言。其所宜从。在于问解。而宋时烈,朴世采之说。益明且备。以此为正庶乎。不背于古礼。然丧纪至重。礼意甚微。更令儒臣。博考古典及诸儒之说。反覆参究。立定条制。恐合审处之道。伏惟 上裁。俞正基妻离异当否议
夫妇。五伦之始。三纲之本。夫妇正而后。伦纲可得以叙也。圣人立七去之法。以明正家之义。若妇有恶行。而夫不敢去。虽至于悖伦乱常。而惟以不相离为道理。则得不有伤于伦纲乎。东方之俗。女子贞信。一适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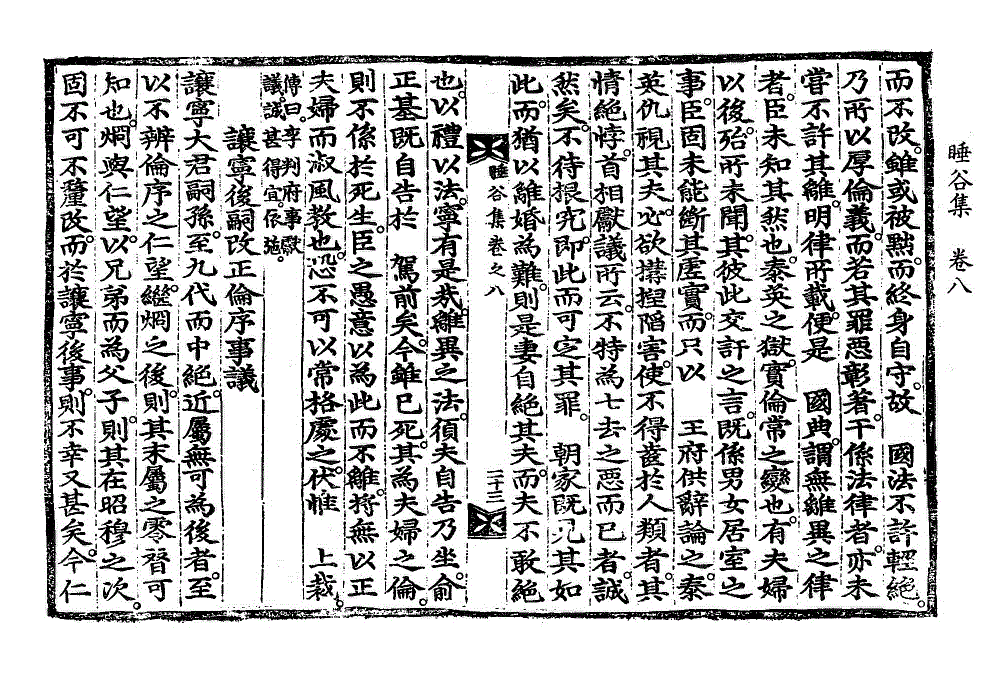 而不改。虽或被黜。而终身自守。故 国法不许轻绝。乃所以厚伦义。而若其罪恶彰著。干系法律者。亦未尝不许其离。明律所载。便是 国典。谓无离异之律者。臣未知其然也。泰英之狱。实伦常之变也。有夫妇以后。殆所未闻。其彼此交讦之言。既系男女居室之事。臣固未能断其虚实。而只以 王府供辞论之。泰英仇视其夫。必欲搆捏陷害。使不得齿于人类者。其情绝悖。首相献议所云。不特为七去之恶而已者。诚然矣。不待根究。即此而可定其罪。 朝家既见其如此。而犹以离婚为难。则是妻自绝其夫。而夫不敢绝也。以礼以法。宁有是哉。离异之法。须夫自告乃坐。俞正基既自告于 驾前矣。今虽已死。其为夫妇之伦。则不系于死生。臣之愚意以为此而不离。将无以正夫妇而淑风教也。恐不可以常格处之。伏惟 上裁。(传曰。李判府事献议。诚甚得宜。依施。)
而不改。虽或被黜。而终身自守。故 国法不许轻绝。乃所以厚伦义。而若其罪恶彰著。干系法律者。亦未尝不许其离。明律所载。便是 国典。谓无离异之律者。臣未知其然也。泰英之狱。实伦常之变也。有夫妇以后。殆所未闻。其彼此交讦之言。既系男女居室之事。臣固未能断其虚实。而只以 王府供辞论之。泰英仇视其夫。必欲搆捏陷害。使不得齿于人类者。其情绝悖。首相献议所云。不特为七去之恶而已者。诚然矣。不待根究。即此而可定其罪。 朝家既见其如此。而犹以离婚为难。则是妻自绝其夫。而夫不敢绝也。以礼以法。宁有是哉。离异之法。须夫自告乃坐。俞正基既自告于 驾前矣。今虽已死。其为夫妇之伦。则不系于死生。臣之愚意以为此而不离。将无以正夫妇而淑风教也。恐不可以常格处之。伏惟 上裁。(传曰。李判府事献议。诚甚得宜。依施。)让宁后嗣改正伦序事议
让宁大君嗣孙。至九代而中绝。近属无可为后者。至以不辨伦序之仁望。继炯之后。则其末属之零替可知也。炯与仁望。以兄弟而为父子。则其在昭穆之次。固不可不釐改。而于让宁后事。则不幸又甚矣。今仁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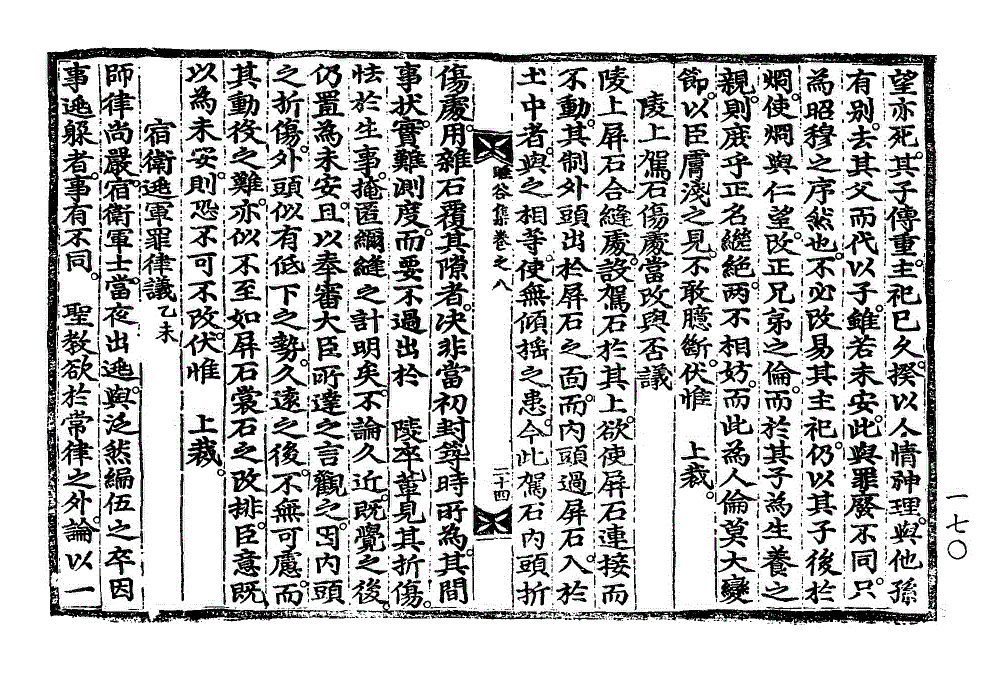 望亦死。其子传重。主祀已久。揆以人情神理。与他孙有别。去其父而代以子。虽若未安。此与罪废不同。只为昭穆之序然也。不必改易其主祀。仍以其子后于炯。使炯与仁望。改正兄弟之伦。而于其子为生养之亲。则庶乎正名继绝。两不相妨。而此为人伦莫大变节。以臣肤浅之见。不敢臆断。伏惟 上裁。
望亦死。其子传重。主祀已久。揆以人情神理。与他孙有别。去其父而代以子。虽若未安。此与罪废不同。只为昭穆之序然也。不必改易其主祀。仍以其子后于炯。使炯与仁望。改正兄弟之伦。而于其子为生养之亲。则庶乎正名继绝。两不相妨。而此为人伦莫大变节。以臣肤浅之见。不敢臆断。伏惟 上裁。陵上驾石伤处当改与否议
陵上屏石合缝处。设驾石于其上。欲使屏石连接而不动。其制外头出于屏石之面。而内头过屏石。入于土中者。与之相等。使无倾摇之患。今此驾石内头折伤处。用杂石覆其隙者。决非当初封筑时所为。其间事状。实难测度。而要不过出于 陵卒辈见其折伤。怯于生事。掩匿弥缝之计明矣。不论久近。既觉之后。仍置为未安。且以奉审大臣所达之言观之。固内头之折伤。外头似有低下之势。久远之后。不无可虑。而其动役之难。亦似不至如屏石裳石之改排。臣意既以为未安。则恐不可不改。伏惟 上裁。
宿卫逃军罪律议(乙未)
师律尚严。宿卫军士。当夜出逃。与泛然编伍之卒因事逃躲者。事有不同。 圣教欲于常律之外。论以一
睡谷先生集卷之八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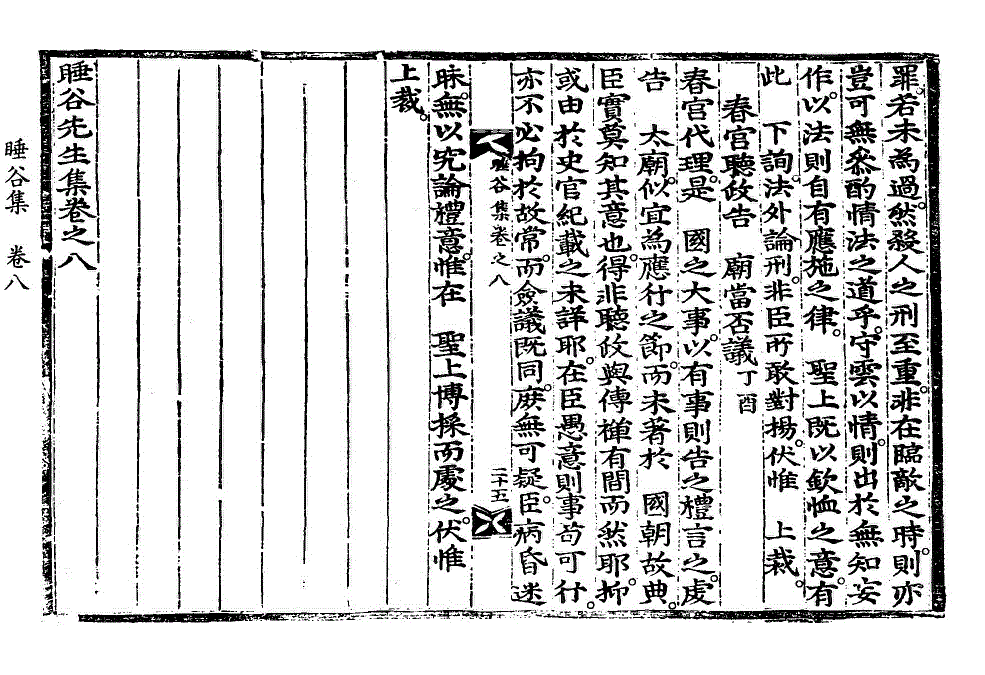 罪。若未为过。然杀人之刑至重。非在临敌之时。则亦岂可无参酌情法之道乎。守云以情。则出于无知妄作。以法则自有应施之律。 圣上既以钦恤之意。有此 下询。法外论刑。非臣所敢对扬。伏惟 上裁。
罪。若未为过。然杀人之刑至重。非在临敌之时。则亦岂可无参酌情法之道乎。守云以情。则出于无知妄作。以法则自有应施之律。 圣上既以钦恤之意。有此 下询。法外论刑。非臣所敢对扬。伏惟 上裁。春宫听政告 庙当否议(丁酉)
春宫代理。是 国之大事。以有事则告之礼言之。虔告 太庙。似宜为应行之节。而未著于 国朝故典。臣实莫知其意也。得非听政与传禅有间而然耶。抑或由于史官纪载之未详耶。在臣愚意则事苟可行。亦不必拘于故常。而佥议既同。庶无可疑。臣病昏迷昧。无以究论礼意。惟在 圣上博采而处之。伏唯 上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