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x 页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论语○子罕
答申明允
他人见孔子。却甚高远。而回也仰瞻。只在前后。但未在中间。为不达一间也。然则此中间是何地位耶。
中间是过与不及之中间。即所谓中也。以地位言则圣人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论语○阳货
答申明允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寻常以为天命未绝于周。夫子之心。盖在尊王室矣。近见伊川说。谓周道衰微。君臣上下。无复伦纪。故夫子发此叹而言不为东周也。今当从伊川耶。
不为东周。非但伊川说如此。诸家说亦然。惟古注曰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疏曰兴周道于东方。使鲁为周。朱子不用伊川说。而一从古注。辅氏曰鲁在周之东故云尔。如获用焉。不兴周道以继文武不已也。以此观之。所谓东周。非平王东迁以后之东周也。言
答问○经义○论语○子罕
答申明允
他人见孔子。却甚高远。而回也仰瞻。只在前后。但未在中间。为不达一间也。然则此中间是何地位耶。
中间是过与不及之中间。即所谓中也。以地位言则圣人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论语○阳货
答申明允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寻常以为天命未绝于周。夫子之心。盖在尊王室矣。近见伊川说。谓周道衰微。君臣上下。无复伦纪。故夫子发此叹而言不为东周也。今当从伊川耶。
不为东周。非但伊川说如此。诸家说亦然。惟古注曰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疏曰兴周道于东方。使鲁为周。朱子不用伊川说。而一从古注。辅氏曰鲁在周之东故云尔。如获用焉。不兴周道以继文武不已也。以此观之。所谓东周。非平王东迁以后之东周也。言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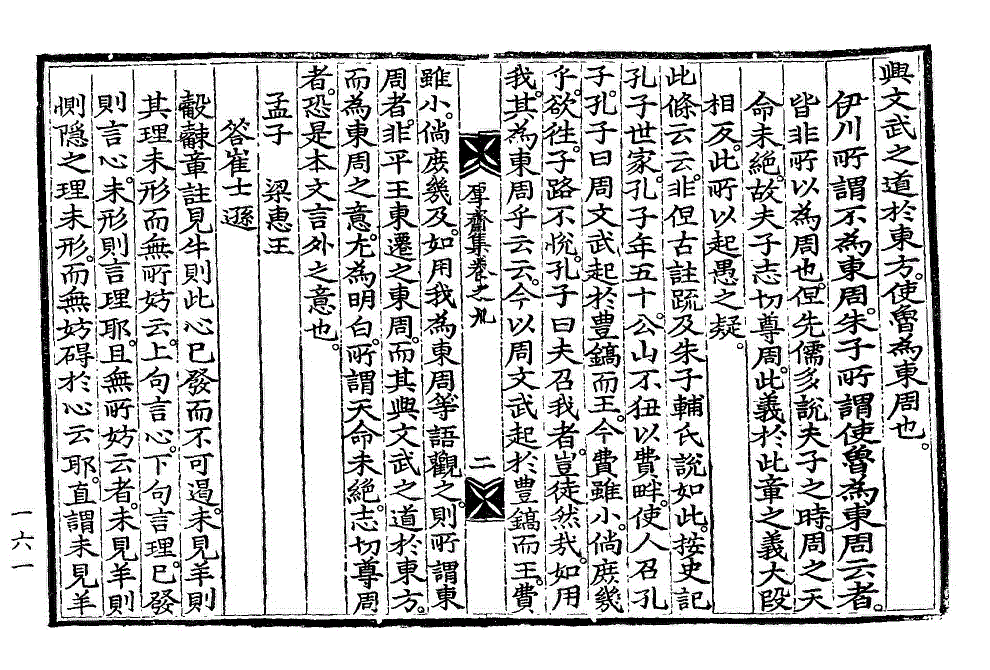 兴文武之道于东方。使鲁为东周也。
兴文武之道于东方。使鲁为东周也。伊川所谓不为东周。朱子所谓使鲁为东周云者。皆非所以为周也。但先儒多说夫子之时。周之天命未绝。故夫子志切尊周。此义于此章之义大段相反。此所以起愚之疑。
此条云云。非但古注疏及朱子辅氏说如此。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于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往。子路不悦。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然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云云。今以周文武起于丰镐而王。费虽小。倘庶几及。如用我为东周等语观之。则所谓东周者。非平王东迁之东周。而其兴文武之道于东方。而为东周之意。尤为明白。所谓天命未绝。志切尊周者。恐是本文言外之意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孟子○梁惠王
答崔士逊
觳觫章注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云。上句言心。下句言理。已发则言心。未形则言理耶。且无所妨云者。未见羊则恻隐之理未形。而无妨碍于心云耶。直谓未见羊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2H 页
 则虽杀之无妨云耶。
则虽杀之无妨云耶。言心言理。亦各有主。盖既见牛则此心蔼然已发而不可抑遏。未见羊则其理寂然潜藏而尚未形著。故于已发处以心言。于未形处以理言。无妨即无害也。言既未见羊则其理未形。故虽以羊易牛。而无害于仁云尔。
答在鲁族侄
若大旱之望云霓。朱子注曰云合则雨。虹见则止。无乃望云者愿其雨也。望霓者恐其不雨也。抑霓字只是带说耶。
不雨则无霓。若言霓则有雨可知也。此等处只当轻看。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孟子○公孙丑
答崔士逊
无是馁也者。无是气则道义馁也。
所谓馁者。非谓道义馁也。即是气不充而体馁也。或问无是馁也。是指义是指气。朱子曰这是说气。集注亦曰馁。饥乏而气不充体也。以此等说观之。其非指道义而言者可知矣。
之景丑氏宿焉者。只欲实仲子之言耶。若然则似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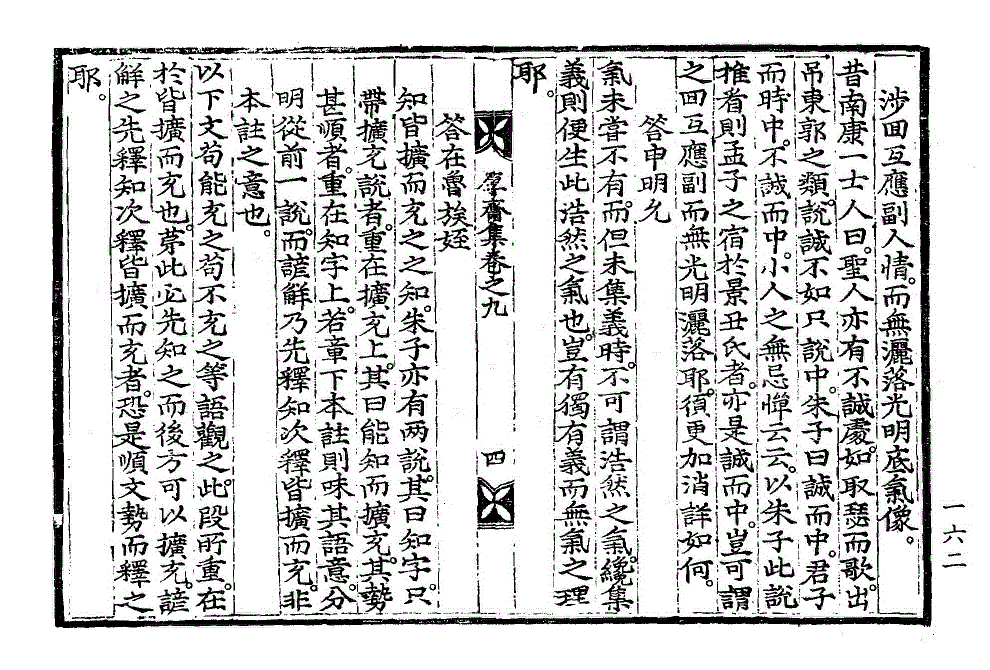 涉回互应副人情。而无洒落光明底气像。
涉回互应副人情。而无洒落光明底气像。昔南康一士人曰。圣人亦有不诚处。如取瑟而歌。出吊东郭之类。说诚不如只说中。朱子曰诚而中。君子而时中。不诚而中。小人之无忌惮云云。以朱子此说推看则孟子之宿于景丑氏者。亦是诚而中。岂可谓之回互应副而无光明洒落耶。须更加消详如何。
答申明允
气未尝不有。而但未集义时。不可谓浩然之气。才集义则便生此浩然之气也。岂有独有义而无气之理耶。
答在鲁族侄
知皆扩而充之之知。朱子亦有两说。其曰知字。只带扩充说者。重在扩充上。其曰能知而扩充。其势甚顺者。重在知字上。若章下本注则味其语意。分明从前一说。而谚解乃先释知次释皆扩而充。非本注之意也。
以下文苟能充之苟不充之等语观之。此段所重。在于皆扩而充也。第此必先知之而后方可以扩充。谚解之先释知次释皆扩而充者。恐是顺文势而释之耶。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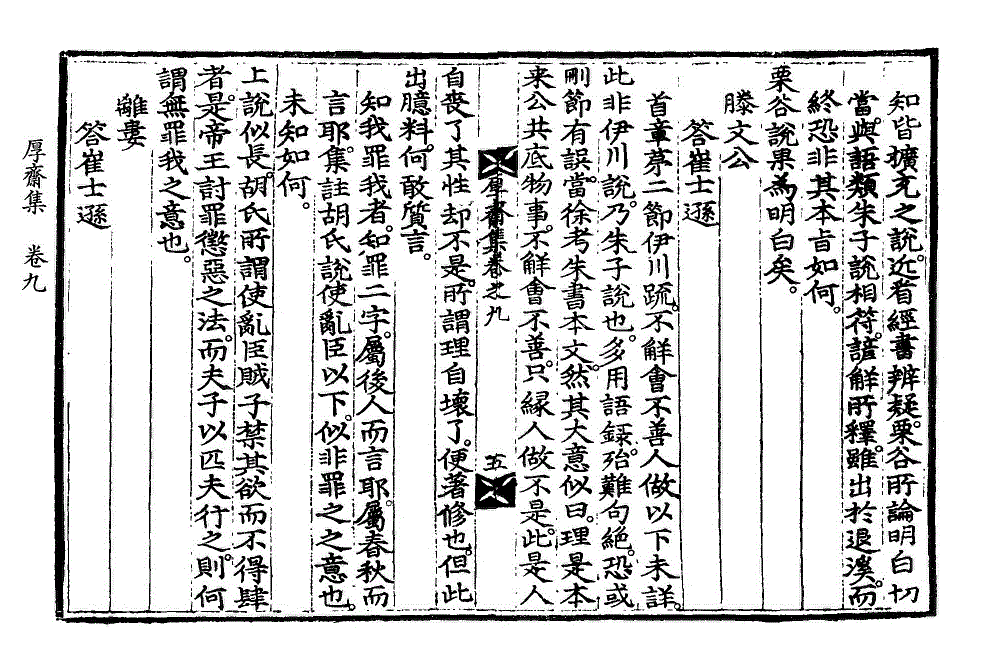 知皆扩充之说。近看经书辨疑。栗谷所论明白切当。与语类朱子说相符。谚解所释。虽出于退溪。而终恐非其本旨如何。
知皆扩充之说。近看经书辨疑。栗谷所论明白切当。与语类朱子说相符。谚解所释。虽出于退溪。而终恐非其本旨如何。栗谷说果为明白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孟子○滕文公
答崔士逊
首章第二节伊川疏。不解会不善人做以下未详。
此非伊川说。乃朱子说也。多用语录。殆难句绝。恐或删节有误。当徐考朱书本文。然其大意似曰。理是本来公共底物事。不解会不善。只缘人做不是。此是人自丧了其性却不是。所谓理自坏了。便著修也。但此出臆料。何敢质言。
知我罪我者。知罪二字。属后人而言耶。属春秋而言耶。集注胡氏说使乱臣以下。似非罪之之意也。未知如何。
上说似长。胡氏所谓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者。是帝王讨罪惩恶之法。而夫子以匹夫行之。则何谓无罪我之意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孟子○离娄
答崔士逊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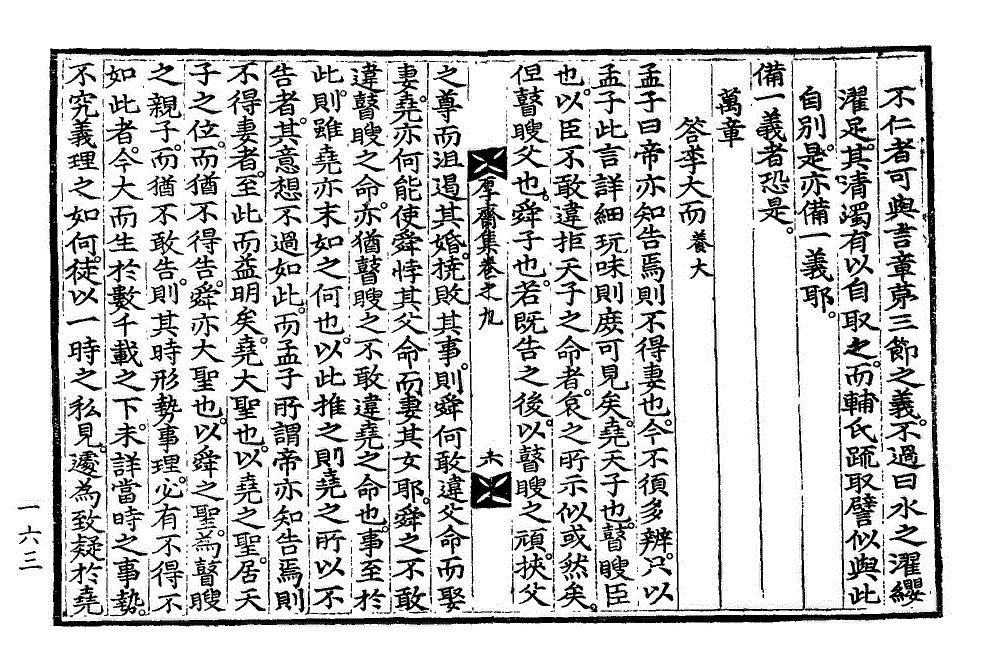 不仁者可与言章第三节之义。不过曰水之濯缨濯足。其清浊有以自取之。而辅氏疏取譬似与此自别。是亦备一义耶。
不仁者可与言章第三节之义。不过曰水之濯缨濯足。其清浊有以自取之。而辅氏疏取譬似与此自别。是亦备一义耶。备一义者恐是。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孟子○万章
答李大而(养大)
孟子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今不须多辨。只以孟子此言详细玩味则庶可见矣。尧天子也。瞽瞍臣也。以臣不敢违拒天子之命者。哀之所示似或然矣。但瞽瞍父也。舜子也。若既告之后。以瞽瞍之顽。挟父之尊而沮遏其婚。挠败其事。则舜何敢违父命而娶妻。尧亦何能使舜悖其父命而妻其女耶。舜之不敢违瞽瞍之命。亦犹瞽瞍之不敢违尧之命也。事至于此。则虽尧亦末如之何也。以此推之则尧之所以不告者。其意想不过如此。而孟子所谓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者。至此而益明矣。尧大圣也。以尧之圣。居天子之位。而犹不得告。舜亦大圣也。以舜之圣。为瞽瞍之亲子。而犹不敢告。则其时形势事理。必有不得不如此者。今大而生于数千载之下。未详当时之事势。不究义理之如何。徒以一时之私见。遽为致疑于尧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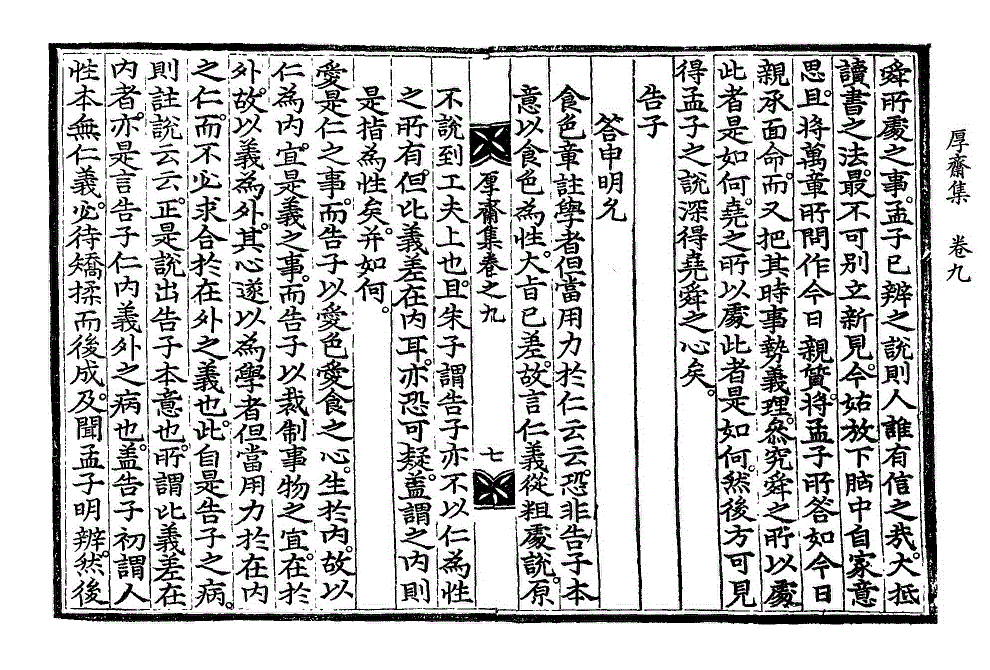 舜所处之事。孟子已辨之说则人谁有信之哉。大抵读书之法。最不可别立新见。今姑放下胸中自家意思。且将万章所问作今日亲质。将孟子所答如今日亲承面命。而又把其时事势义理。参究舜之所以处此者是如何。尧之所以处此者是如何。然后方可见得孟子之说深得尧舜之心矣。
舜所处之事。孟子已辨之说则人谁有信之哉。大抵读书之法。最不可别立新见。今姑放下胸中自家意思。且将万章所问作今日亲质。将孟子所答如今日亲承面命。而又把其时事势义理。参究舜之所以处此者是如何。尧之所以处此者是如何。然后方可见得孟子之说深得尧舜之心矣。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孟子○告子
答申明允
食色章注学者但当用力于仁云云。恐非告子本意以食色为性。大旨已差。故言仁义从粗处说。原不说到工夫上也。且朱子谓告子亦不以仁为性之所有。但比义差在内耳。亦恐可疑。盖谓之内则是指为性矣。并如何。
爱是仁之事。而告子以爱色爱食之心。生于内。故以仁为内。宜是义之事。而告子以裁制事物之宜。在于外。故以义为外。其心遂以为学者但当用力于在内之仁。而不必求合于在外之义也。此自是告子之病。则注说云云。正是说出告子本意也。所谓比义差在内者。亦是言告子仁内义外之病也。盖告子初谓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及闻孟子明辨。然后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4L 页
 略知仁为内。但其为内者。谓比义差在内云耳。
略知仁为内。但其为内者。谓比义差在内云耳。才与情何别。金而精克诚曰四端可以训才耶。此说如何。
四端似非才。其能恻隐能羞恶者恐是才也。
浩然之气。虽是集义而生。然自人之禀生后观之。形贮气气贮理。非形无气。非气无理。故凡言气者。虽夜气浩气。恐或不出于气质圈围之中也。未知如何。
来说似然。第气质二字。语似新奇。徐容更思。
答李君辅
学问之道无他条。栗谷曰求其放心。乃学者工夫之极处。窃谓此段似是记录之误。退溪以为求放心浅言之则固为第一下手着脚处。就其深而极言之则一念少差亦是放云云。若曰通浅深言则可。若曰只指极处言则不可。
所谓而已者。只是言学问之道。惟求放心之外更无他道云尔。栗谷工夫极处之说。似是记录之误。退溪浅深之言。亦是推衍之说。非孟子本文之意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孟子○尽心
答崔士逊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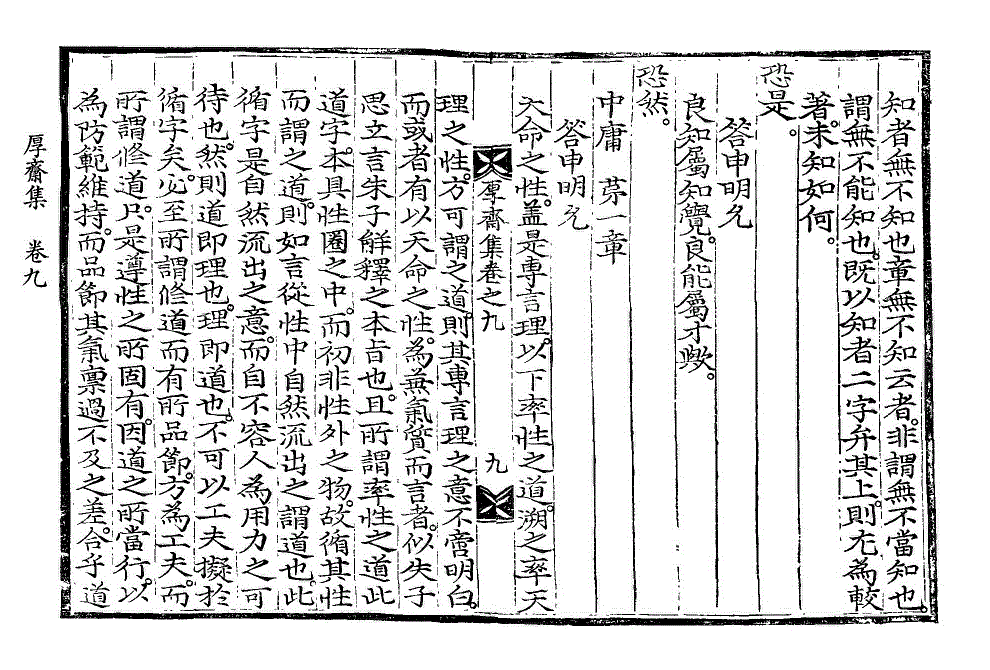 知者无不知也章无不知云者。非谓无不当知也。谓无不能知也。既以知者二字弁其上。则尤为较著。未知如何。
知者无不知也章无不知云者。非谓无不当知也。谓无不能知也。既以知者二字弁其上。则尤为较著。未知如何。恐是。
答申明允
良知属知觉。良能属才欤。
恐然。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一章
答申明允
天命之性。盖是专言理。以下率性之道。溯之率天理之性。方可谓之道。则其专言理之意不啻明白。而或者有以天命之性。为兼气质而言者。似失子思立言朱子解释之本旨也。且所谓率性之道此道字。本具性圈之中。而初非性外之物。故循其性而谓之道。则如言从性中自然流出之谓道也。此循字是自然流出之意。而自不容人为用力之可待也。然则道即理也。理即道也。不可以工夫拟于循字矣。必至所谓修道而有所品节。方为工夫。而所谓修道。只是遵性之所固有。因道之所当行。以为防范维持。而品节其气禀过不及之差。合乎道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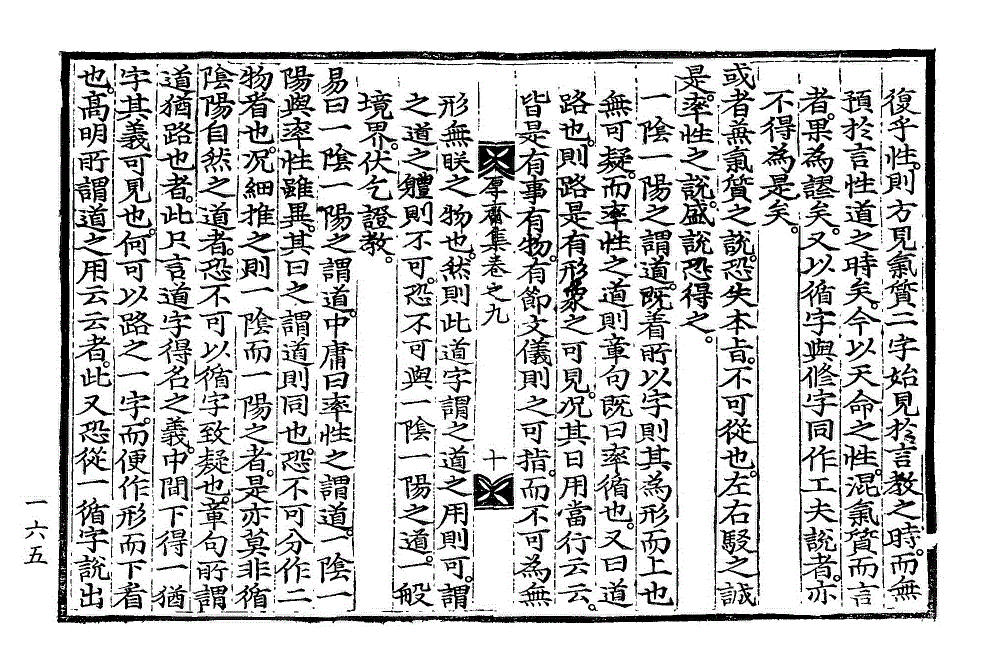 复乎性。则方见气质二字始见于言教之时。而无预于言性道之时矣。今以天命之性。混气质而言者。果为谬矣。又以循字与修字同作工夫说者。亦不得为是矣。
复乎性。则方见气质二字始见于言教之时。而无预于言性道之时矣。今以天命之性。混气质而言者。果为谬矣。又以循字与修字同作工夫说者。亦不得为是矣。或者兼气质之说。恐失本旨。不可从也。左右驳之诚是。率性之说。盛说恐得之。
一阴一阳之谓道。既着所以字则其为形而上也无可疑。而率性之道则章句既曰率循也。又曰道路也。则路是有形象之可见。况其日用当行云云。皆是有事有物。有节文仪则之可指。而不可为无形无眹之物也。然则此道字谓之道之用则可。谓之道之体则不可。恐不可与一阴一阳之道。一般境界。伏乞證教。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曰率性之谓道。一阴一阳与率性虽异。其曰之谓道则同也。恐不可分作二物看也。况细推之则一阴而一阳之者。是亦莫非循阴阳自然之道者。恐不可以循字致疑也。章句所谓道犹路也者。此只言道字得名之义。中间下得一犹字其义可见也。何可以路之一字。而便作形而下看也。高明所谓道之用云云者。此又恐从一循字说出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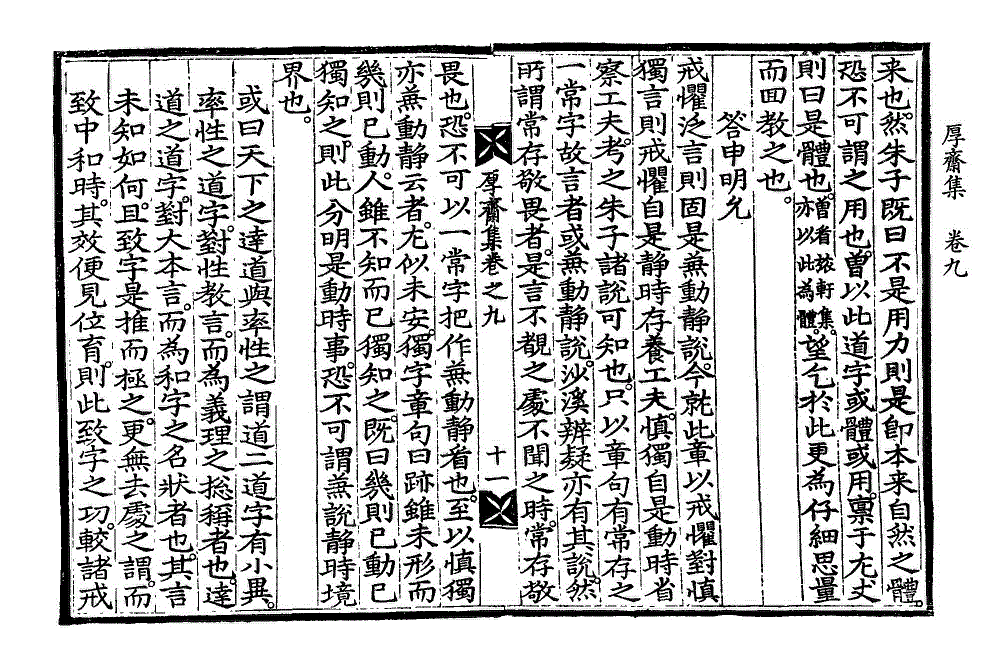 来也。然朱子既曰不是用力则是即本来自然之体。恐不可谓之用也。曾以此道字或体或用。禀于尤丈则曰是体也。(曾看旅轩集。亦以此为体。)望乞于此更为仔细思量而回教之也。
来也。然朱子既曰不是用力则是即本来自然之体。恐不可谓之用也。曾以此道字或体或用。禀于尤丈则曰是体也。(曾看旅轩集。亦以此为体。)望乞于此更为仔细思量而回教之也。答申明允
戒惧泛言则固是兼动静说。今就此章以戒惧对慎独言则戒惧自是静时存养工夫。慎独自是动时省察工夫。考之朱子诸说可知也。只以章句有常存之一常字故言者或兼动静说。沙溪辨疑亦有其说。然所谓常存敬畏者。是言不睹之处不闻之时。常存敬畏也。恐不可以一常字把作兼动静看也。至以慎独亦兼动静云者。尤似未安。独字章句曰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既曰几则已动己独知之。则此分明是动时事。恐不可谓兼说静时境界也。
或曰天下之达道与率性之谓道二道字有小异。率性之道字。对性教言。而为义理之总称者也。达道之道字。对大本言。而为和字之名状者也。其言未知如何。且致字是推而极之。更无去处之谓。而致中和时。其效便见位育。则此致字之功。较诸戒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6L 页
 惧谨独。似有先后生熟之分。未知然否。
惧谨独。似有先后生熟之分。未知然否。率性之道与达道之道。初非二道也。但率性之道。以人物之各循其性者言也。达道之道。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言也。其言虽似少异。而其理未尝不同也。戒惧谨独。是致中和位育之工夫也。致中和位育。是戒惧谨独之功效也。此只当以工夫功效言之。恐不必以生熟分言也。
答宋基孙
以天命之性章句观之。人物皆禀五常之德无疑。天之生万物。只是浑然一个理也。总言则一理。分言则五常。初无件数面貌之不同。然则天之生物。物之禀赋。宁有择其优劣贵贱而有间哉。特以既生之后。拘于形气。人则气清而理全。物则气塞而理亦偏。自外面观之则蜂蚁之君臣。虎狼之父子。似乎各得一理之偏。而论其本原则宁有多少分数乎。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者。政指此也。近来诸家皆以为人则禀五常之性。物则只禀一理云。愿闻的礭之教。
来示甚是。足以破近来一种纷纭之说也。
答李汝恢(廓)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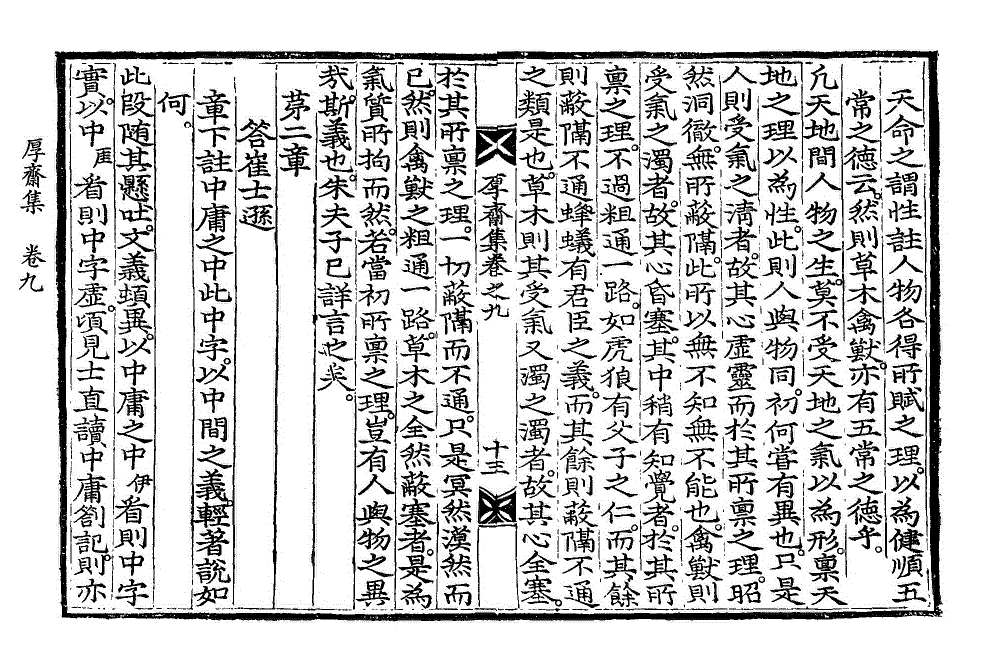 天命之谓性注人物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云。然则草木禽兽。亦有五常之德乎。
天命之谓性注人物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云。然则草木禽兽。亦有五常之德乎。凡天地间人物之生。莫不受天地之气以为形。禀天地之理以为性。此则人与物同。初何尝有异也。只是人则受气之清者。故其心虚灵而于其所禀之理。昭然洞彻。无所蔽隔。此所以无不知无不能也。禽兽则受气之浊者。故其心昏塞。其中稍有知觉者。于其所禀之理。不过粗通一路。如虎狼有父子之仁。而其馀则蔽隔不通。蜂蚁有君臣之义。而其馀则蔽隔不通之类是也。草木则其受气又浊之浊者。故其心全塞。于其所禀之理。一切蔽隔而不通。只是冥然漠然而已。然则禽兽之粗通一路。草木之全然蔽塞者。是为气质所拘而然。若当初所禀之理。岂有人与物之异哉。斯义也。朱夫子已详言之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二章
答崔士逊
章下注中庸之中此中字。以中间之义。轻著说如何。
此段随其悬吐。文义顿异。以中庸之中(伊)看则中字实。以中(厓)看则中字虚。顷见士直读中庸劄记。则亦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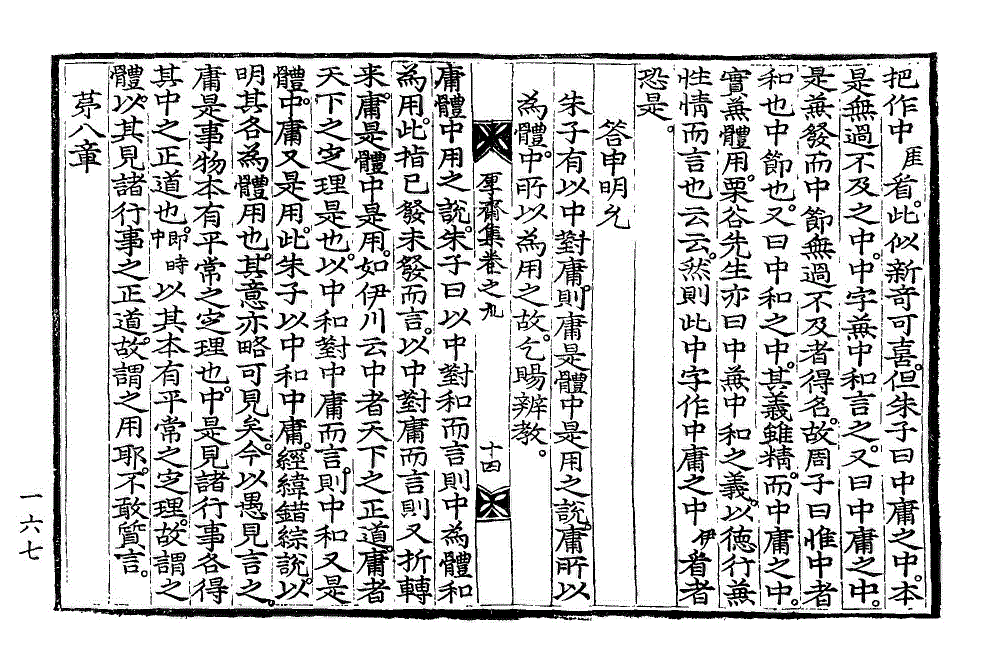 把作中(厓)看。此似新奇可喜。但朱子曰中庸之中。本是无过不及之中。中字兼中和言之。又曰中庸之中。是兼发而中节无过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节也。又曰中和之中。其义虽精。而中庸之中。实兼体用。栗谷先生亦曰中兼中和之义。以德行兼性情而言也云云。然则此中字作中庸之中(伊)看者恐是。
把作中(厓)看。此似新奇可喜。但朱子曰中庸之中。本是无过不及之中。中字兼中和言之。又曰中庸之中。是兼发而中节无过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节也。又曰中和之中。其义虽精。而中庸之中。实兼体用。栗谷先生亦曰中兼中和之义。以德行兼性情而言也云云。然则此中字作中庸之中(伊)看者恐是。答申明允
朱子有以中对庸。则庸是体中是用之说。庸所以为体。中所以为用之故。乞赐辨教。
庸体中用之说。朱子曰以中对和而言则中为体和为用。此指已发未发而言。以中对庸而言则又折转来。庸是体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此朱子以中和中庸。经纬错综说。以明其各为体用也。其意亦略可见矣。今以愚见言之。庸是事物本有平常之定理也。中是见诸行事各得其中之正道也。(即时中)以其本有平常之定理。故谓之体。以其见诸行事之正道。故谓之用耶。不敢质言。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八章
答申明允
得一善云者。是取诸人为善之意耶。是行道而有得于心之意耶。
蓝田吕氏曰。颜子随其所至。尽其所得。据而守之则拳拳服膺不敢失。朱子以吕说为亲切礭实。以此观之。就心上说者似优耶。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十一章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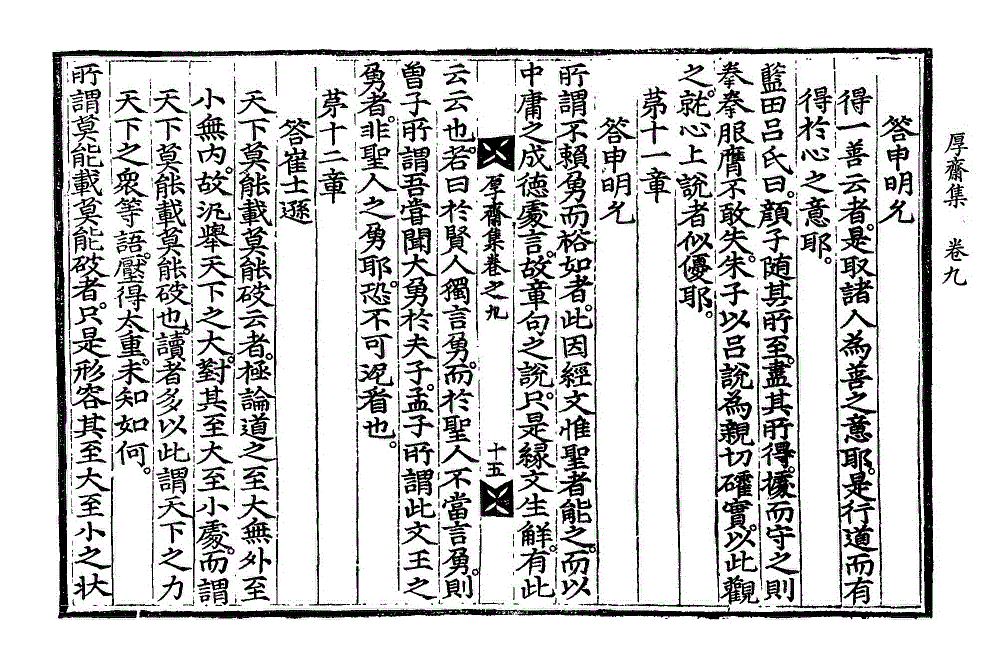 答申明允
答申明允所谓不赖勇而裕如者。此因经文惟圣者能之。而以中庸之成德处言。故章句之说。只是缘文生解。有此云云也。若曰于贤人独言勇。而于圣人不当言勇。则曾子所谓吾尝闻大勇于夫子。孟子所谓此文王之勇者。非圣人之勇耶。恐不可泥看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十二章
答崔士逊
天下莫能载莫能破云者。极论道之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故汎举天下之大。对其至大至小处。而谓天下莫能载莫能破也。读者多以此谓天下之力天下之众等语。压得太重。未知如何。
所谓莫能载莫能破者。只是形容其至大至小之状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8L 页
 而已。或者之说。恐失本旨。
而已。或者之说。恐失本旨。章句所引程子说吃紧为人处云者。以子思举鸢鱼明化育流行之妙者。为人开示处甚紧切也。活泼泼地云者。专论化育流行之体。不滞于一隅。而活泼流动底意思。且两句间只句切勿悬吐。下句下以悬吐读则似宛转如何。
恐是。
答申明允
费隐。以道之体用而言。则纯理而不杂于气。故即费即隐。皆属形而上之界。而不落形而下之机矣。以太极言之则无极而太极为隐。而万物各具一太极为费。以性命言之则率性之道为费。而天命之性为隐。以一贯言之则万殊者为费。而一本者为隐否。
来示恐然。
自一物言之。其性为隐也。为理一也。其运动发用而性之直遂者为费也。为分殊也。
指性之微妙难见处为隐。不可以隐。直谓之性也。指用之无所不在者谓费。不可以费。直谓之用也。此一段。恐欠精当。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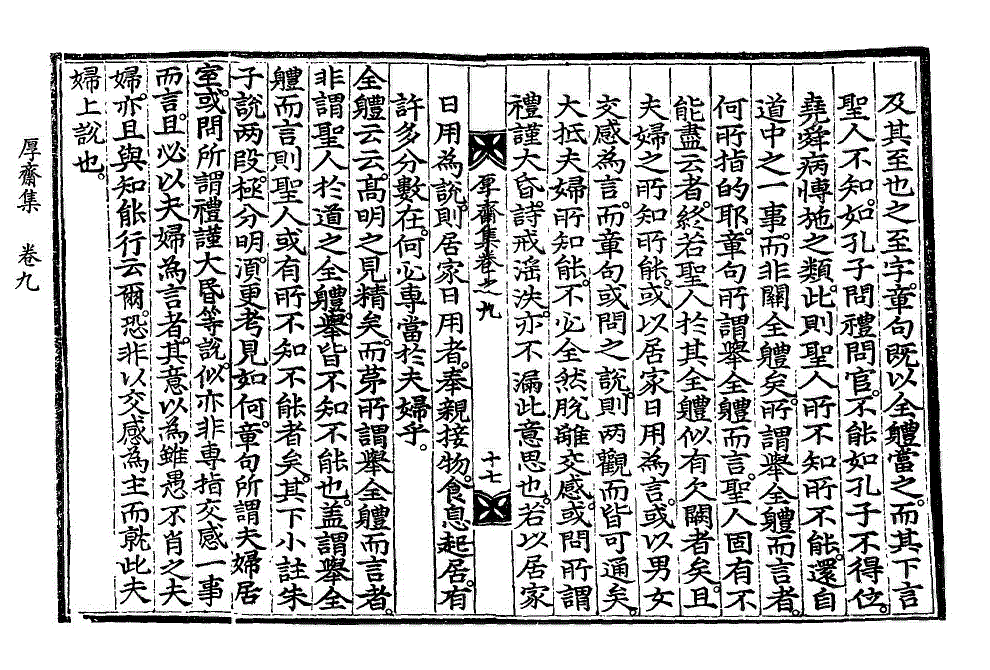 及其至也之至字。章句既以全体当之。而其下言圣人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尧舜病博施之类。此则圣人所不知所不能。还自道中之一事。而非关全体矣。所谓举全体而言者。何所指的耶。章句所谓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不能尽云者。终若圣人于其全体似有欠阙者矣。且夫妇之所知所能。或以居家日用为言。或以男女交感为言。而章句或问之说。则两观而皆可通矣。大抵夫妇所知能。不必全然脱离交感。或问所谓礼谨大昏。诗戒淫泆。亦不漏此意思也。若以居家日用为说。则居家日用者。奉亲接物。食息起居。有许多分数在。何必专当于夫妇乎。
及其至也之至字。章句既以全体当之。而其下言圣人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尧舜病博施之类。此则圣人所不知所不能。还自道中之一事。而非关全体矣。所谓举全体而言者。何所指的耶。章句所谓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不能尽云者。终若圣人于其全体似有欠阙者矣。且夫妇之所知所能。或以居家日用为言。或以男女交感为言。而章句或问之说。则两观而皆可通矣。大抵夫妇所知能。不必全然脱离交感。或问所谓礼谨大昏。诗戒淫泆。亦不漏此意思也。若以居家日用为说。则居家日用者。奉亲接物。食息起居。有许多分数在。何必专当于夫妇乎。全体云云。高明之见精矣。而第所谓举全体而言者。非谓圣人于道之全体。举皆不知不能也。盖谓举全体而言则圣人或有所不知不能者矣。其下小注朱子说两段。极分明。须更考见如何。章句所谓夫妇居室。或问所谓礼谨大昏等说。似亦非专指交感一事而言。且必以夫妇为言者。其意以为虽愚不肖之夫妇。亦且与知能行云尔。恐非以交感为主而就此夫妇上说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十三章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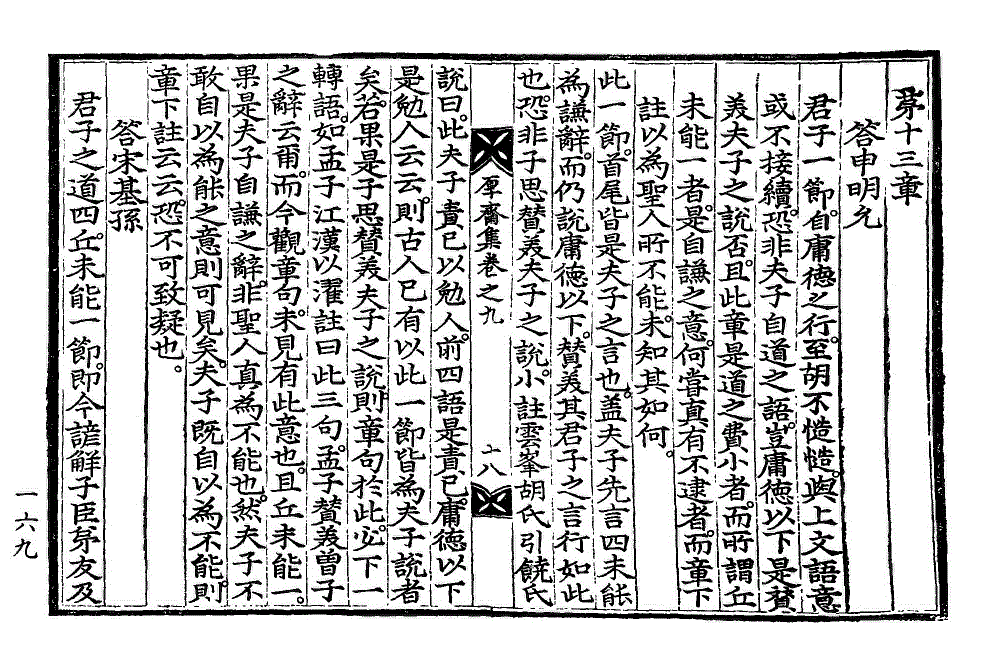 答申明允
答申明允君子一节。自庸德之行。至胡不慥慥。与上文语意或不接续。恐非夫子自道之语。岂庸德以下是赞美夫子之说否。且此章是道之费小者。而所谓丘未能一者。是自谦之意。何尝真有不逮者。而章下注以为圣人所不能。未知其如何。
此一节。首尾皆是夫子之言也。盖夫子先言四未能为谦辞。而仍说庸德以下。赞美其君子之言行如此也。恐非子思赞美夫子之说。小注云峰胡氏引饶氏说曰。此夫子责己以勉人。前四语是责己。庸德以下是勉人云云。则古人已有以此一节皆为夫子说者矣。若果是子思赞美夫子之说。则章句于此。必下一转语。如孟子江汉以濯注曰此三句。孟子赞美曾子之辞云尔。而今观章句。未见有此意也。且丘未能一。果是夫子自谦之辞。非圣人真为不能也。然夫子不敢自以为能之意则可见矣。夫子既自以为不能。则章下注云云。恐不可致疑也。
答宋基孙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节。即今谚解子臣弟友及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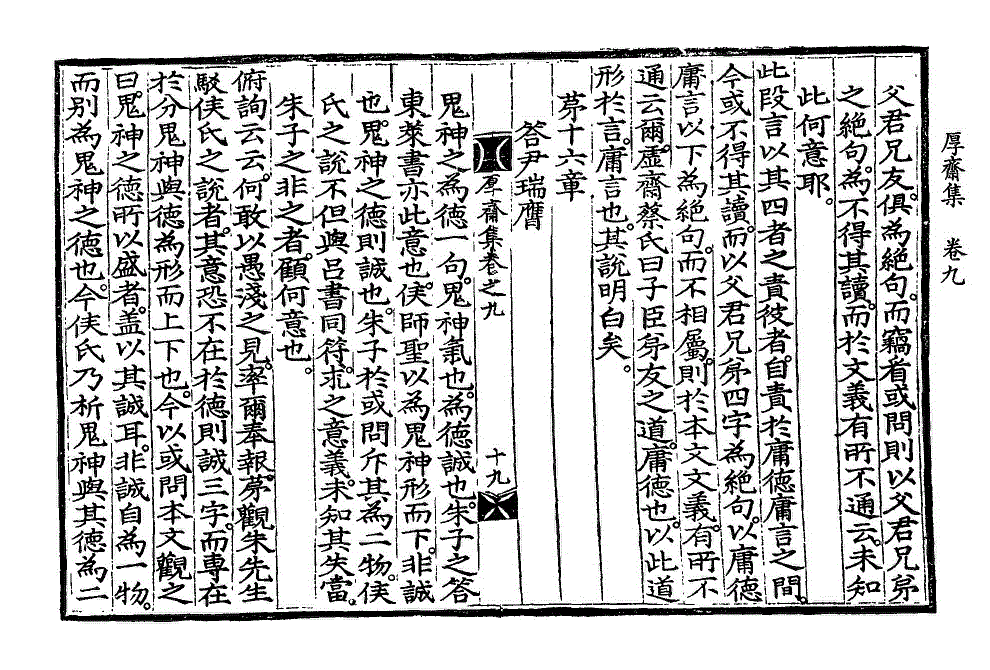 父君兄友。俱为绝句。而窃看或问则以父君兄弟之绝句。为不得其读。而于文义有所不通云。未知此何意耶。
父君兄友。俱为绝句。而窃看或问则以父君兄弟之绝句。为不得其读。而于文义有所不通云。未知此何意耶。此段言以其四者之责彼者。自责于庸德庸言之间。今或不得其读。而以父君兄弟四字为绝句。以庸德庸言以下为绝句。而不相属。则于本文文义。有所不通云尔。虚斋蔡氏曰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形于言。庸言也。其说明白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十六章
答尹瑞膺
鬼神之为德一句。鬼神气也。为德诚也。朱子之答东莱书亦此意也。侯师圣以为鬼神形而下。非诚也。鬼神之德则诚也。朱子于或问斥其为二物。侯氏之说不但与吕书同符。求之意义。未知其失当。朱子之非之者。顾何意也。
俯询云云。何敢以愚浅之见。率尔奉报。第观朱先生驳侯氏之说者。其意恐不在于德则诚三字。而专在于分鬼神与德为形而上下也。今以或问本文观之曰。鬼神之德所以盛者。盖以其诚耳。非诚自为一物。而别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与其德为二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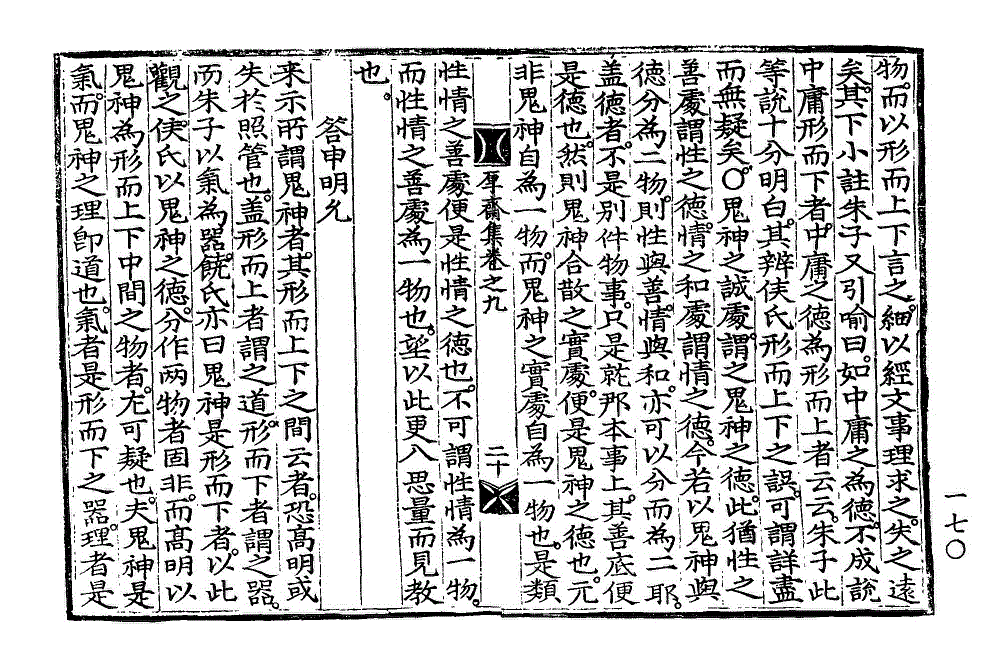 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细以经文事理求之。失之远矣。其下小注朱子又引喻曰。如中庸之为德。不成说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为形而上者云云。朱子此等说十分明白。其辨侯氏形而上下之误。可谓详尽而无疑矣。○鬼神之诚处。谓之鬼神之德。此犹性之善处谓性之德。情之和处谓情之德。今若以鬼神与德分为二物。则性与善。情与和。亦可以分而为二耶。盖德者。不是别件物事。只是就那本事上。其善底便是德也。然则鬼神合散之实处。便是鬼神之德也。元非鬼神自为一物。而鬼神之实处自为一物也。是类性情之善处便是性情之德也。不可谓性情为一物。而性情之善处为一物也。望以此更入思量而见教也。
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细以经文事理求之。失之远矣。其下小注朱子又引喻曰。如中庸之为德。不成说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为形而上者云云。朱子此等说十分明白。其辨侯氏形而上下之误。可谓详尽而无疑矣。○鬼神之诚处。谓之鬼神之德。此犹性之善处谓性之德。情之和处谓情之德。今若以鬼神与德分为二物。则性与善。情与和。亦可以分而为二耶。盖德者。不是别件物事。只是就那本事上。其善底便是德也。然则鬼神合散之实处。便是鬼神之德也。元非鬼神自为一物。而鬼神之实处自为一物也。是类性情之善处便是性情之德也。不可谓性情为一物。而性情之善处为一物也。望以此更入思量而见教也。答申明允
来示所谓鬼神者。其形而上下之间云者。恐高明或失于照管也。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朱子以气为器。饶氏亦曰鬼神是形而下者。以此观之。侯氏以鬼神之德。分作两物者固非。而高明以鬼神为形而上下中间之物者。尤可疑也。夫鬼神是气。而鬼神之理即道也。气者是形而下之器。理者是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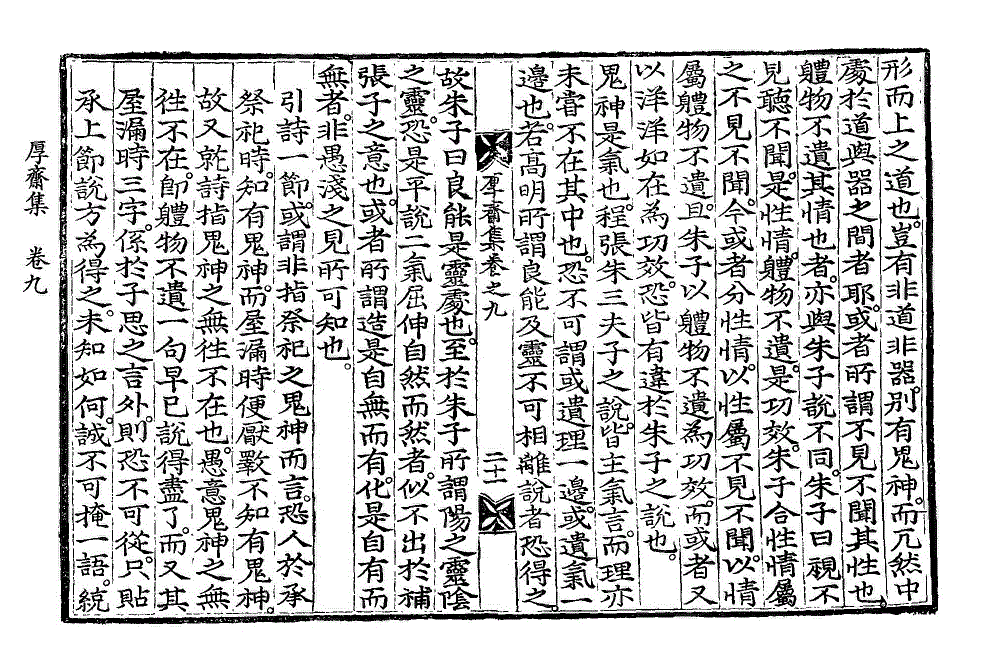 形而上之道也。岂有非道非器。别有鬼神。而兀然中处于道与器之间者耶。或者所谓不见不闻其性也。体物不遗其情也者。亦与朱子说不同。朱子曰视不见听不闻。是性情。体物不遗。是功效。朱子合性情属之不见不闻。今或者分性情。以性属不见不闻。以情属体物不遗。且朱子以体物不遗为功效。而或者又以洋洋如在为功效。恐皆有违于朱子之说也。鬼神是气也。程张朱三夫子之说。皆主气言。而理亦未尝不在其中也。恐不可谓或遗理一边。或遗气一边也。若高明所谓良能及灵不可相离说者恐得之。故朱子曰良能是灵处也。至于朱子所谓阳之灵阴之灵。恐是平说二气屈伸自然而然者。似不出于补张子之意也。或者所谓造是自无而有。化是自有而无者。非愚浅之见所可知也。
形而上之道也。岂有非道非器。别有鬼神。而兀然中处于道与器之间者耶。或者所谓不见不闻其性也。体物不遗其情也者。亦与朱子说不同。朱子曰视不见听不闻。是性情。体物不遗。是功效。朱子合性情属之不见不闻。今或者分性情。以性属不见不闻。以情属体物不遗。且朱子以体物不遗为功效。而或者又以洋洋如在为功效。恐皆有违于朱子之说也。鬼神是气也。程张朱三夫子之说。皆主气言。而理亦未尝不在其中也。恐不可谓或遗理一边。或遗气一边也。若高明所谓良能及灵不可相离说者恐得之。故朱子曰良能是灵处也。至于朱子所谓阳之灵阴之灵。恐是平说二气屈伸自然而然者。似不出于补张子之意也。或者所谓造是自无而有。化是自有而无者。非愚浅之见所可知也。引诗一节。或谓非指祭祀之鬼神而言。恐人于承祭祀时。知有鬼神。而屋漏时便厌斁不知有鬼神。故又就诗指鬼神之无往不在也。愚意鬼神之无往不在。即体物不遗一句早已说得尽了。而又其屋漏时三字。系于子思之言外。则恐不可从。只贴承上节说方为得之。未知如何。诚不可掩一语。统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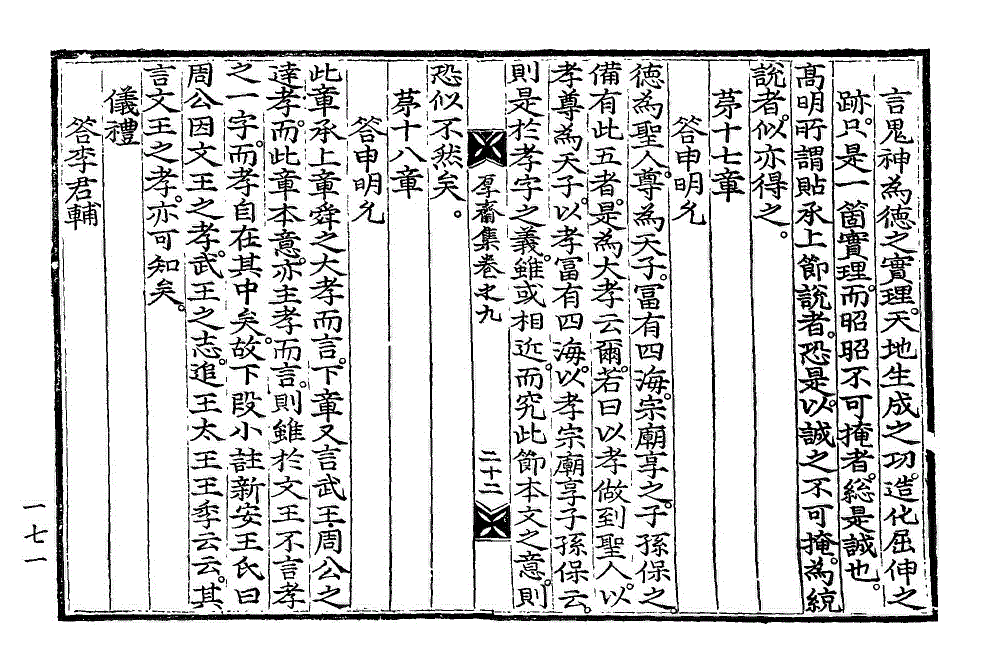 言鬼神为德之实理。天地生成之功。造化屈伸之迹。只是一个实理。而昭昭不可掩者。总是诚也。
言鬼神为德之实理。天地生成之功。造化屈伸之迹。只是一个实理。而昭昭不可掩者。总是诚也。高明所谓贴承上节说者。恐是。以诚之不可掩。为统说者。似亦得之。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十七章
答申明允
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备有此五者。是为大孝云尔。若曰以孝做到圣人。以孝尊为天子。以孝富有四海。以孝宗庙享子孙保云。则是于孝字之义。虽或相近。而究此节本文之意。则恐似不然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中庸○第十八章
答申明允
此章承上章舜之大孝而言。下章又言武王,周公之达孝。而此章本意。亦主孝而言。则虽于文王不言孝之一字。而孝自在其中矣。故下段小注新安王氏曰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太王王季云云。其言文王之孝。亦可知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答问○经义○仪礼
答李君辅
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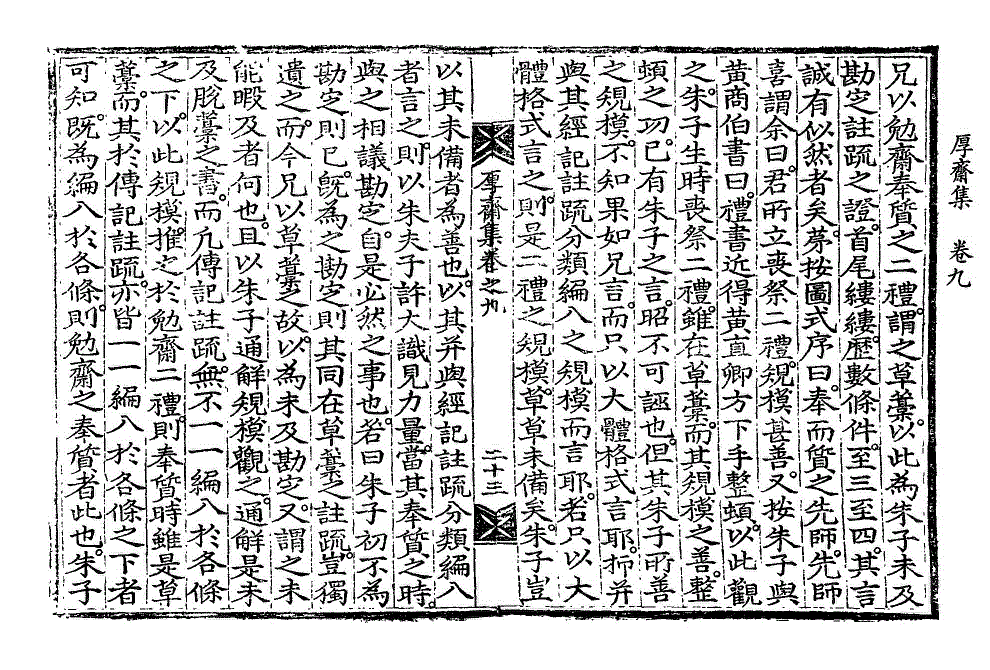 兄以勉斋奉质之二礼。谓之草稿。以此为朱子未及勘定注疏之證。首尾缕缕。历数条件。至三至四。其言诚有似然者矣。第按图式序曰。奉而质之先师。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二礼。规模甚善。又按朱子与黄商伯书曰。礼书近得黄直卿方下手整顿。以此观之。朱子生时丧祭二礼。虽在草稿。而其规模之善。整顿之功。已有朱子之言。昭不可诬也。但其朱子所善之规模。不知果如兄言。而只以大体格式言耶。抑并与其经记注疏分类编入之规模而言耶。若只以大体格式言之。则是二礼之规模。草草未备矣。朱子岂以其未备者为善也。以其并与经记注疏分类编入者言之。则以朱夫子许大识见力量。当其奉质之时。与之相议勘定。自是必然之事也。若曰朱子初不为勘定则已。既为之勘定则其同在草稿之注疏。岂独遗之。而今兄以草稿之故。以为未及勘定。又谓之未能暇及者何也。且以朱子通解规模观之。通解是未及脱稿之书。而凡传记注疏。无不一一编入于各条之下。以此规模。推之于勉斋二礼。则奉质时虽是草稿。而其于传记注疏。亦皆一一编入于各条之下者可知。既为编入于各条。则勉斋之奉质者此也。朱子
兄以勉斋奉质之二礼。谓之草稿。以此为朱子未及勘定注疏之證。首尾缕缕。历数条件。至三至四。其言诚有似然者矣。第按图式序曰。奉而质之先师。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二礼。规模甚善。又按朱子与黄商伯书曰。礼书近得黄直卿方下手整顿。以此观之。朱子生时丧祭二礼。虽在草稿。而其规模之善。整顿之功。已有朱子之言。昭不可诬也。但其朱子所善之规模。不知果如兄言。而只以大体格式言耶。抑并与其经记注疏分类编入之规模而言耶。若只以大体格式言之。则是二礼之规模。草草未备矣。朱子岂以其未备者为善也。以其并与经记注疏分类编入者言之。则以朱夫子许大识见力量。当其奉质之时。与之相议勘定。自是必然之事也。若曰朱子初不为勘定则已。既为之勘定则其同在草稿之注疏。岂独遗之。而今兄以草稿之故。以为未及勘定。又谓之未能暇及者何也。且以朱子通解规模观之。通解是未及脱稿之书。而凡传记注疏。无不一一编入于各条之下。以此规模。推之于勉斋二礼。则奉质时虽是草稿。而其于传记注疏。亦皆一一编入于各条之下者可知。既为编入于各条。则勉斋之奉质者此也。朱子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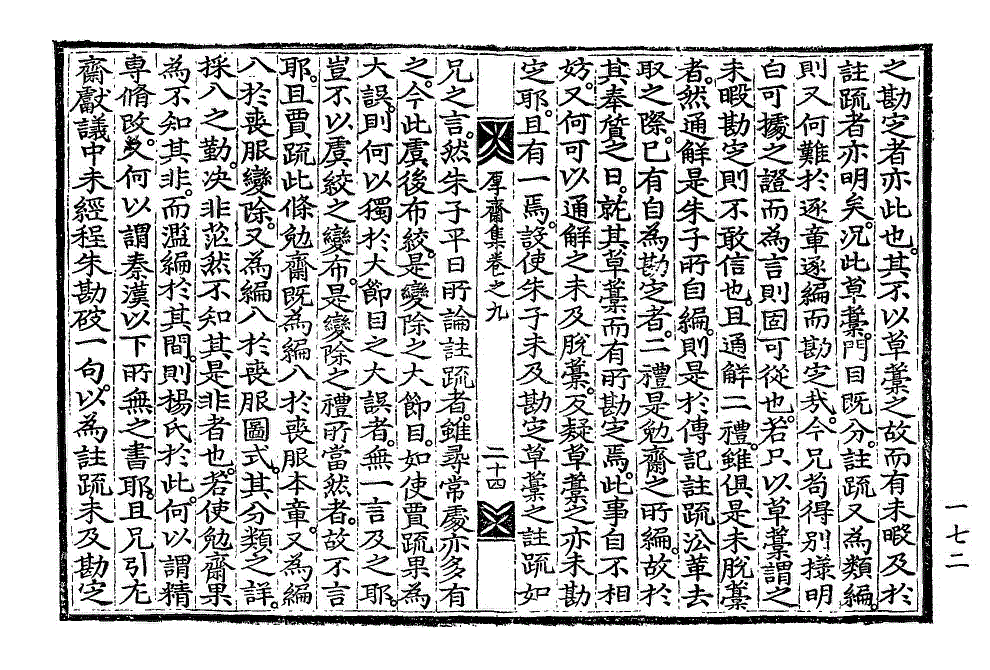 之勘定者亦此也。其不以草稿之故而有未暇及于注疏者亦明矣。况此草稿。门目既分。注疏又为类编。则又何难于逐章逐编而勘定哉。今兄苟得别样明白可据之證而为言则固可从也。若只以草稿谓之未暇勘定则不敢信也。且通解二礼。虽俱是未脱稿者。然通解是朱子所自编。则是于传记注疏沿革去取之际。已有自为勘定者。二礼是勉斋之所编。故于其奉质之日。就其草稿而有所勘定焉。此事自不相妨。又何可以通解之未及脱稿。反疑草稿之亦未勘定耶。且有一焉。设使朱子未及勘定草稿之注疏如兄之言。然朱子平日所论注疏者。虽寻常处亦多有之。今此虞后布绞。是变除之大节目。如使贾疏果为大误。则何以独于大节目之大误者。无一言及之耶。岂不以虞绞之变布。是变除之礼所当然者。故不言耶。且贾疏此条勉斋既为编入于丧服本章。又为编入于丧服变除。又为编入于丧服图式。其分类之详。采入之勤。决非茫然不知其是非者也。若使勉斋果为不知其非。而滥编于其间。则杨氏于此。何以谓精专脩改。又何以谓秦汉以下所无之书耶。且兄引尤斋献议中未经程朱勘破一句。以为注疏未及勘定
之勘定者亦此也。其不以草稿之故而有未暇及于注疏者亦明矣。况此草稿。门目既分。注疏又为类编。则又何难于逐章逐编而勘定哉。今兄苟得别样明白可据之證而为言则固可从也。若只以草稿谓之未暇勘定则不敢信也。且通解二礼。虽俱是未脱稿者。然通解是朱子所自编。则是于传记注疏沿革去取之际。已有自为勘定者。二礼是勉斋之所编。故于其奉质之日。就其草稿而有所勘定焉。此事自不相妨。又何可以通解之未及脱稿。反疑草稿之亦未勘定耶。且有一焉。设使朱子未及勘定草稿之注疏如兄之言。然朱子平日所论注疏者。虽寻常处亦多有之。今此虞后布绞。是变除之大节目。如使贾疏果为大误。则何以独于大节目之大误者。无一言及之耶。岂不以虞绞之变布。是变除之礼所当然者。故不言耶。且贾疏此条勉斋既为编入于丧服本章。又为编入于丧服变除。又为编入于丧服图式。其分类之详。采入之勤。决非茫然不知其是非者也。若使勉斋果为不知其非。而滥编于其间。则杨氏于此。何以谓精专脩改。又何以谓秦汉以下所无之书耶。且兄引尤斋献议中未经程朱勘破一句。以为注疏未及勘定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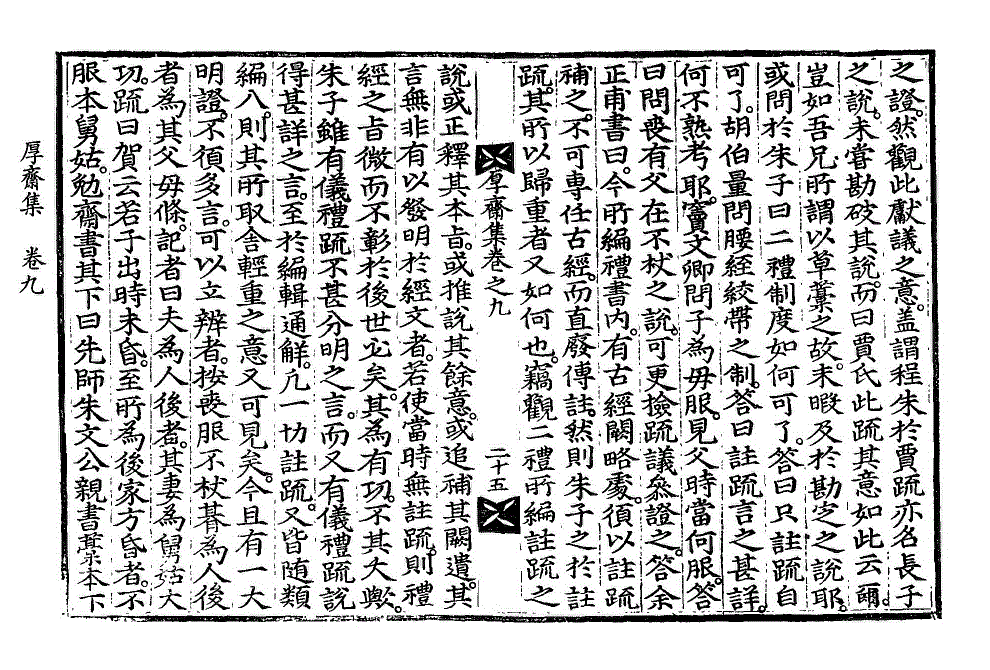 之證。然观此献议之意。盖谓程朱于贾疏亦名长子之说。未尝勘破其说。而曰贾氏此疏其意如此云尔。岂如吾兄所谓以草稿之故。未暇及于勘定之说耶。或问于朱子曰二礼制度如何可了。答曰只注疏自可了。胡伯量问腰绖绞带之制。答曰注疏言之甚详。何不熟考耶。窦文卿问子为母服。见父时当何服。答曰问丧有父在不杖之说。可更检疏议参證之。答余正甫书曰。今所编礼书内。有古经阙略处。须以注疏补之。不可专任古经。而直废传注。然则朱子之于注疏。其所以归重者又如何也。窃观二礼所编注疏之说或正释其本旨。或推说其馀意。或追补其阙遗。其言无非有以发明于经文者。若使当时无注疏。则礼经之旨微而不彰于后世必矣。其为有功。不其大欤。朱子虽有仪礼疏不甚分明之言。而又有仪礼疏说得甚详之言。至于编辑通解。凡一切注疏。又皆随类编入。则其所取舍轻重之意又可见矣。今且有一大明證。不须多言。可以立辨者。按丧服不杖期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条。记者曰夫为人后者。其妻为舅姑大功。疏曰贺云若子出时未昏。至所为后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勉斋书其下曰先师朱文公亲书稿本下
之證。然观此献议之意。盖谓程朱于贾疏亦名长子之说。未尝勘破其说。而曰贾氏此疏其意如此云尔。岂如吾兄所谓以草稿之故。未暇及于勘定之说耶。或问于朱子曰二礼制度如何可了。答曰只注疏自可了。胡伯量问腰绖绞带之制。答曰注疏言之甚详。何不熟考耶。窦文卿问子为母服。见父时当何服。答曰问丧有父在不杖之说。可更检疏议参證之。答余正甫书曰。今所编礼书内。有古经阙略处。须以注疏补之。不可专任古经。而直废传注。然则朱子之于注疏。其所以归重者又如何也。窃观二礼所编注疏之说或正释其本旨。或推说其馀意。或追补其阙遗。其言无非有以发明于经文者。若使当时无注疏。则礼经之旨微而不彰于后世必矣。其为有功。不其大欤。朱子虽有仪礼疏不甚分明之言。而又有仪礼疏说得甚详之言。至于编辑通解。凡一切注疏。又皆随类编入。则其所取舍轻重之意又可见矣。今且有一大明證。不须多言。可以立辨者。按丧服不杖期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条。记者曰夫为人后者。其妻为舅姑大功。疏曰贺云若子出时未昏。至所为后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勉斋书其下曰先师朱文公亲书稿本下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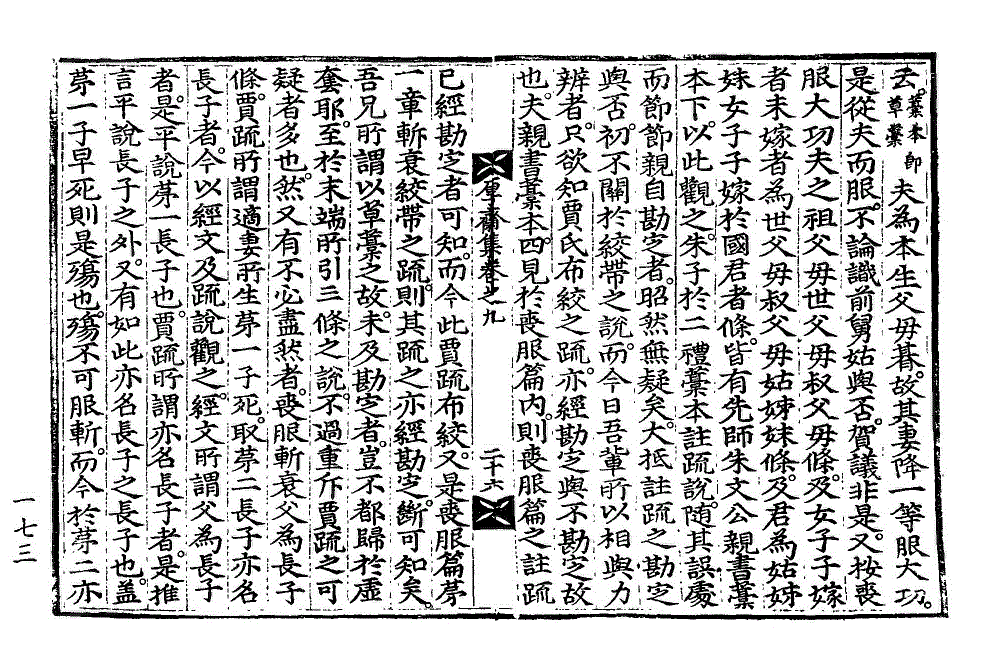 云。(稿本即草稿)夫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从夫而服。不论识前舅姑与否。贺议非是。又按丧服大功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条。及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条。及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条。皆有先师朱文公亲书稿本下。以此观之。朱子于二礼稿本注疏说。随其误处而节节亲自勘定者。昭然无疑矣。大抵注疏之勘定与否。初不关于绞带之说。而今日吾辈所以相与力辨者。只欲知贾氏布绞之疏。亦经勘定与不勘定故也。夫亲书稿本。四见于丧服篇内。则丧服篇之注疏已经勘定者可知。而今此贾疏布绞。又是丧服篇第一章斩衰绞带之疏。则其疏之亦经勘定。断可知矣。吾兄所谓以草稿之故。未及勘定者。岂不都归于虚套耶。至于末端所引三条之说。不过重斥贾疏之可疑者多也。然又有不必尽然者。丧服斩衰父为长子条。贾疏所谓适妻所生第一子死。取第二长子亦名长子者。今以经文及疏说观之。经文所谓父为长子者。是平说第一长子也。贾疏所谓亦名长子者。是推言平说长子之外。又有如此亦名长子之长子也。盖第一子早死则是殇也。殇不可服斩。而今于第二亦
云。(稿本即草稿)夫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从夫而服。不论识前舅姑与否。贺议非是。又按丧服大功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条。及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条。及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条。皆有先师朱文公亲书稿本下。以此观之。朱子于二礼稿本注疏说。随其误处而节节亲自勘定者。昭然无疑矣。大抵注疏之勘定与否。初不关于绞带之说。而今日吾辈所以相与力辨者。只欲知贾氏布绞之疏。亦经勘定与不勘定故也。夫亲书稿本。四见于丧服篇内。则丧服篇之注疏已经勘定者可知。而今此贾疏布绞。又是丧服篇第一章斩衰绞带之疏。则其疏之亦经勘定。断可知矣。吾兄所谓以草稿之故。未及勘定者。岂不都归于虚套耶。至于末端所引三条之说。不过重斥贾疏之可疑者多也。然又有不必尽然者。丧服斩衰父为长子条。贾疏所谓适妻所生第一子死。取第二长子亦名长子者。今以经文及疏说观之。经文所谓父为长子者。是平说第一长子也。贾疏所谓亦名长子者。是推言平说长子之外。又有如此亦名长子之长子也。盖第一子早死则是殇也。殇不可服斩。而今于第二亦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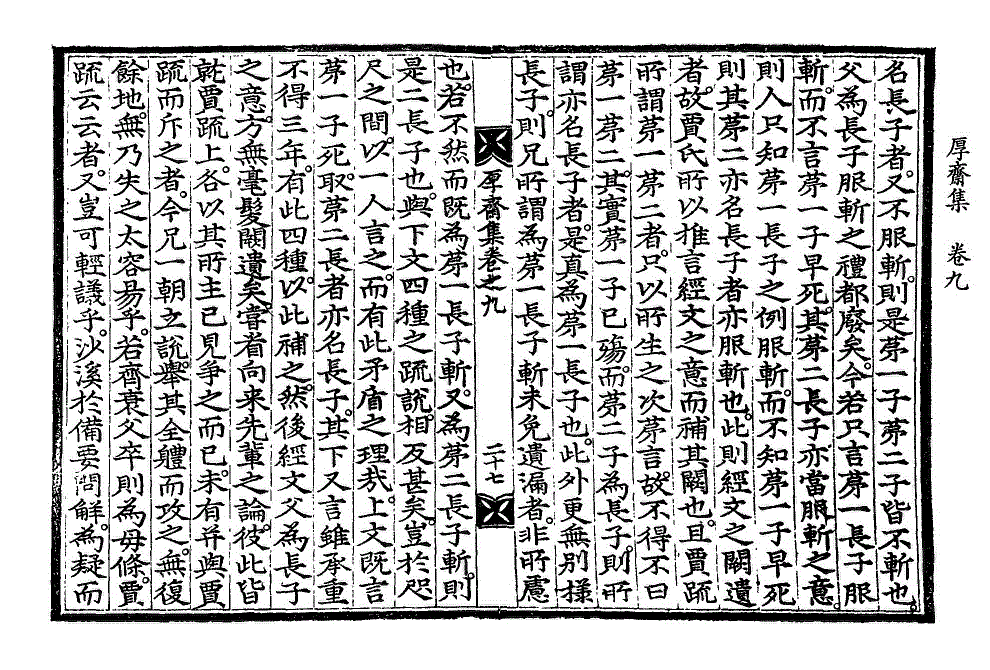 名长子者。又不服斩。则是第一子第二子皆不斩也。父为长子服斩之礼都废矣。今若只言第一长子服斩。而不言第一子早死。其第二长子亦当服斩之意。则人只知第一长子之例服斩。而不知第一子早死则其第二亦名长子者亦服斩也。此则经文之阙遗者。故贾氏所以推言经文之意而补其阙也。且贾疏所谓第一第二者。只以所生之次第言。故不得不曰第一第二。其实第一子已殇。而第二子为长子。则所谓亦名长子者。是真为第一长子也。此外更无别样长子。则兄所谓为第一长子斩未免遗漏者。非所虑也。若不然而既为第一长子斩。又为第二长子斩。则是二长子也。与下文四种之疏说。相反甚矣。岂于咫尺之间。以一人言之。而有此矛盾之理哉。上文既言第一子死。取第二长者亦名长子。其下又言虽承重不得三年。有此四种。以此补之。然后经文父为长子之意。方无毫发阙遗矣。尝看向来先辈之论。彼此皆就贾疏上。各以其所主已见争之而已。未有并与贾疏而斥之者。今兄一朝立说。举其全体而攻之。无复馀地。无乃失之太容易乎。若齐衰父卒则为母条。贾疏云云者。又岂可轻议乎。沙溪于备要问解。为疑而
名长子者。又不服斩。则是第一子第二子皆不斩也。父为长子服斩之礼都废矣。今若只言第一长子服斩。而不言第一子早死。其第二长子亦当服斩之意。则人只知第一长子之例服斩。而不知第一子早死则其第二亦名长子者亦服斩也。此则经文之阙遗者。故贾氏所以推言经文之意而补其阙也。且贾疏所谓第一第二者。只以所生之次第言。故不得不曰第一第二。其实第一子已殇。而第二子为长子。则所谓亦名长子者。是真为第一长子也。此外更无别样长子。则兄所谓为第一长子斩未免遗漏者。非所虑也。若不然而既为第一长子斩。又为第二长子斩。则是二长子也。与下文四种之疏说。相反甚矣。岂于咫尺之间。以一人言之。而有此矛盾之理哉。上文既言第一子死。取第二长者亦名长子。其下又言虽承重不得三年。有此四种。以此补之。然后经文父为长子之意。方无毫发阙遗矣。尝看向来先辈之论。彼此皆就贾疏上。各以其所主已见争之而已。未有并与贾疏而斥之者。今兄一朝立说。举其全体而攻之。无复馀地。无乃失之太容易乎。若齐衰父卒则为母条。贾疏云云者。又岂可轻议乎。沙溪于备要问解。为疑而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4L 页
 未决之辞。而尝于答洪校理霶之问。有父卒三年之内母卒。仍服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祥十五月禫祭脱衰心丧。古礼然矣。人谁有非之者之说。(见家礼辑览并有丧条)又尝见先师父死为祖为母异服议曰。通典贺循曰父死未殡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殡而祖父死三年。仪礼通解丧服疏曰。父卒三年之内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卒乃得申三年。此皆人子不忍死其亲之意。而为祖则既殡而申三年。为母则要父服除而申三年。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其为祖也。虽其父才卒。而所重在承重。故以既殡为节。其为母也。虽父死已久。而所重在尊父。故以服除为节。此其或重或轻。情义委曲。又答士直之问曰。丧服父卒则为母疏。父卒三年之内母卒则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申三年云者。原于经文。成于疏义。定于通解续。證于丧服图。皆无二辞。则恐难以沙溪未定之说而废之也。又曰以父之尊。犹为子三年而后娶。以子之卑。不待父三年除丧而先自尽服于母。或反有歉于尊父也云云。今观沙溪于此。虽为两项说。而先师所论。其言十分明白痛快严正。真可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弟尝禀于尤丈曰。今有父死才殡。而其母踵亡
未决之辞。而尝于答洪校理霶之问。有父卒三年之内母卒。仍服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祥十五月禫祭脱衰心丧。古礼然矣。人谁有非之者之说。(见家礼辑览并有丧条)又尝见先师父死为祖为母异服议曰。通典贺循曰父死未殡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殡而祖父死三年。仪礼通解丧服疏曰。父卒三年之内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卒乃得申三年。此皆人子不忍死其亲之意。而为祖则既殡而申三年。为母则要父服除而申三年。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其为祖也。虽其父才卒。而所重在承重。故以既殡为节。其为母也。虽父死已久。而所重在尊父。故以服除为节。此其或重或轻。情义委曲。又答士直之问曰。丧服父卒则为母疏。父卒三年之内母卒则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申三年云者。原于经文。成于疏义。定于通解续。證于丧服图。皆无二辞。则恐难以沙溪未定之说而废之也。又曰以父之尊。犹为子三年而后娶。以子之卑。不待父三年除丧而先自尽服于母。或反有歉于尊父也云云。今观沙溪于此。虽为两项说。而先师所论。其言十分明白痛快严正。真可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弟尝禀于尤丈曰。今有父死才殡。而其母踵亡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5H 页
 者。或曰母亡既在父死后。当申三年之服。或曰是在父丧三年内。即同之平存宜服期。两说孰是。答曰在古礼可考也。仪礼丧服章齐衰父卒则为母条。疏曰云则者。欲见父卒三年之内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后母死乃得申。以此观之。当服期云云。见此尤丈答说。其意亦可见矣。且兄引小记母卒则不服之说一段。而以此母卒则字之无他义。證丧服父卒则字之亦无他义。其言似矣。而亦有不然者。盖丧服所谓父卒则为母者。有尊父之义甚重。而小记所谓母卒则不服者。只是言母卒则不服之义而已。此文势同而意义异者也。考诸经传中。亦有此例。如君正莫不正。再见于孟子。而其意则异。夫君正莫不正。全文同而意犹不同。何可以卒则二字之同。而不究其本旨之有异耶。若嗣举奠条郑氏注曰。嗣主人将为后者。其下贾疏所谓不言适而言将为后。欲见无长适。立庶子及同宗为后皆是云云者。盖其意以为举奠自是长适嗣之事。而若无长适则虽庶子及同宗之将为后而嗣者。当举奠云尔。此亦推说经文之意。而终又不失于郑注将为后之本意也。且兄引或者之言曰勉斋编次续解时。本文注疏支辞蔓语之外。不欲
者。或曰母亡既在父死后。当申三年之服。或曰是在父丧三年内。即同之平存宜服期。两说孰是。答曰在古礼可考也。仪礼丧服章齐衰父卒则为母条。疏曰云则者。欲见父卒三年之内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后母死乃得申。以此观之。当服期云云。见此尤丈答说。其意亦可见矣。且兄引小记母卒则不服之说一段。而以此母卒则字之无他义。證丧服父卒则字之亦无他义。其言似矣。而亦有不然者。盖丧服所谓父卒则为母者。有尊父之义甚重。而小记所谓母卒则不服者。只是言母卒则不服之义而已。此文势同而意义异者也。考诸经传中。亦有此例。如君正莫不正。再见于孟子。而其意则异。夫君正莫不正。全文同而意犹不同。何可以卒则二字之同。而不究其本旨之有异耶。若嗣举奠条郑氏注曰。嗣主人将为后者。其下贾疏所谓不言适而言将为后。欲见无长适。立庶子及同宗为后皆是云云者。盖其意以为举奠自是长适嗣之事。而若无长适则虽庶子及同宗之将为后而嗣者。当举奠云尔。此亦推说经文之意。而终又不失于郑注将为后之本意也。且兄引或者之言曰勉斋编次续解时。本文注疏支辞蔓语之外。不欲厚斋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5L 页
 轻删。依前仍录。故有如此可疑处云云。此又不然。按杨氏序曰先生(勉斋)嘉定己卯归自建邺。取丧礼稿本精专修改。又曰先生之于二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同异之论。以示天下后世。又按朱子曰直卿寓三山。与杨志仁(杨氏字也)反复。所修礼书。具有本末云云。观此则其用工详密而不为粗略苟且者可见矣。况杨氏是勉斋同门之人。而又是同为修整者。则其所谓精专修改。推明辨正等语。皆是亲见其事而亲书者。或者所谓依前仍录。有此可疑者。是无所依据之说也。今兄舍杨氏亲见亲书之言。而欲从或者无所依据之说何也。大抵兄初因攻贾氏布绞一段。而转攻贾疏他说数条。以證贾疏之不可信。又因攻此贾疏。而馀锋转及于黄,杨二先生。以为二礼中误取贾疏之證。一并挥斥。如弃唾洟。辗转延及。少无顾惜。岂非朱子所谓无事中生事。退溪所谓无过中求有过耶。望兄于此更加商量幸甚。
轻删。依前仍录。故有如此可疑处云云。此又不然。按杨氏序曰先生(勉斋)嘉定己卯归自建邺。取丧礼稿本精专修改。又曰先生之于二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同异之论。以示天下后世。又按朱子曰直卿寓三山。与杨志仁(杨氏字也)反复。所修礼书。具有本末云云。观此则其用工详密而不为粗略苟且者可见矣。况杨氏是勉斋同门之人。而又是同为修整者。则其所谓精专修改。推明辨正等语。皆是亲见其事而亲书者。或者所谓依前仍录。有此可疑者。是无所依据之说也。今兄舍杨氏亲见亲书之言。而欲从或者无所依据之说何也。大抵兄初因攻贾氏布绞一段。而转攻贾疏他说数条。以證贾疏之不可信。又因攻此贾疏。而馀锋转及于黄,杨二先生。以为二礼中误取贾疏之證。一并挥斥。如弃唾洟。辗转延及。少无顾惜。岂非朱子所谓无事中生事。退溪所谓无过中求有过耶。望兄于此更加商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