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x 页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序
序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4H 页
 送外兄李仲实(永敷)归香湖序
送外兄李仲实(永敷)归香湖序洞庭七百里。鉴湖三百顷。自古以形胜名天下。遗尘遁世之士。往往游其间。吾东江陵郡有香湖。世传湖有沈香。故云香湖。南北一里。东西数里。周回又七八里。前临渤海。后邻金刚。沙棠岸松。隐映左右。洲禽汀鳞。自在游泳。波光澄碧。景态难状。则此洞庭而未七百。鉴湖而不三百者也。然而自古及今。不知其几千百年。而未闻有一人遗尘遁世。逍遥其间者。余外兄李仲实氏。全城人。故新庵公李俊民之玄孙也。自少魁梧。不与时俗俯仰焉。今年夏忧时势隐民瘼。沥忠肝抗尺疏。谨再拜献于 北阙下。仍大忤时意。遂以是冬。挈妻孥忘世累。乃往宅于玆湖之滨焉。夫千百年所未有者。今忽有焉。则岂所谓遗尘遁世之士者非欤。噫。仲实氏之行。可谓卓卓矣。今亲旧朋知之送其行者。莫不以不合于时而去为叹焉。然吾思之。仲实氏之与时不合。非固有意于不合也。此直而彼曲。此正而彼邪。此公论而彼私意。此善类而彼小人。夫如是则安得而相合欤。况仲实氏以拔群之姿。承家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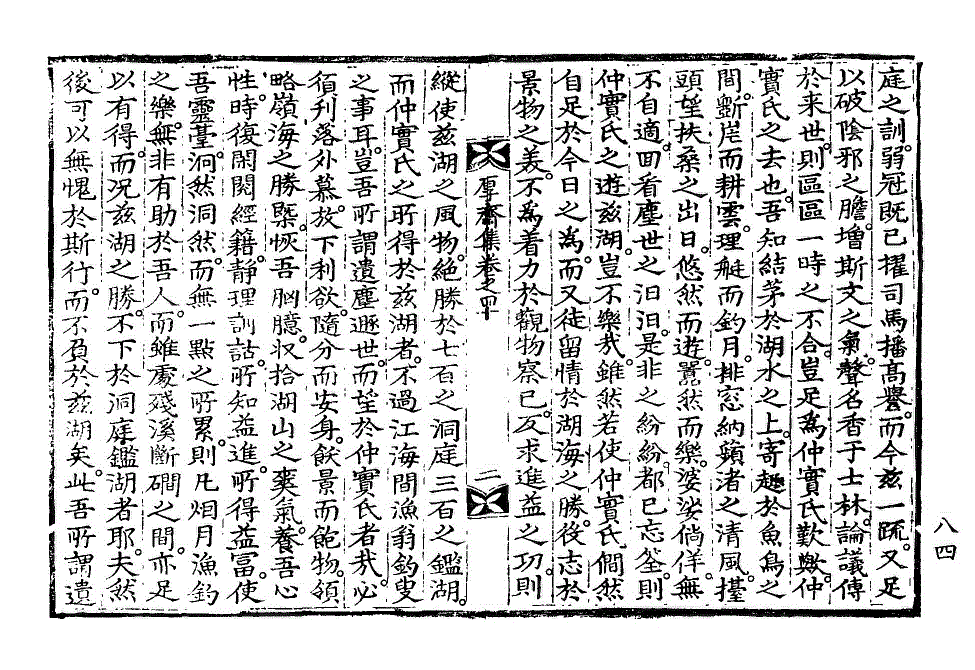 庭之训。弱冠既已擢司马播高誉。而今玆一疏。又足以破阴邪之胆。增斯文之气。声名香于士林。论议传于来世。则区区一时之不合。岂足为仲实氏叹欤。仲实氏之去也。吾知结茅于湖水之上。寄趣于鱼鸟之间。斲岸而耕云。理艇而钓月。排窗纳蘋渚之清风。抬头望扶桑之出日。悠然而游。嚣然而乐。婆娑倘佯。无不自适。回看尘世之汩汩。是非之纷纷。都已忘筌。则仲实氏之游玆湖。岂不乐哉。虽然若使仲实氏僩然自足于今日之为。而又徒留情于湖海之胜。役志于景物之美。不为着力于观物察己。反求进益之功。则纵使玆湖之风物。绝胜于七百之洞庭三百之鉴湖。而仲实氏之所得于玆湖者。不过江海间渔翁钓叟之事耳。岂吾所谓遗尘遁世。而望于仲实氏者哉。必须刊落外慕。放下利欲。随分而安身。饫景而饱物。领略岭海之胜槩。恢吾胸臆。收拾湖山之爽气。养吾心性。时复闲阅经籍。静理训诂。所知益进。所得益富。使吾灵台。泂然洞然。而无一点之所累。则凡烟月渔钓之乐。无非有助于吾人。而虽处残溪断涧之间。亦足以有得。而况玆湖之胜。不下于洞庭,鉴湖者耶。夫然后可以无愧于斯行。而不负于玆湖矣。此吾所谓遗
庭之训。弱冠既已擢司马播高誉。而今玆一疏。又足以破阴邪之胆。增斯文之气。声名香于士林。论议传于来世。则区区一时之不合。岂足为仲实氏叹欤。仲实氏之去也。吾知结茅于湖水之上。寄趣于鱼鸟之间。斲岸而耕云。理艇而钓月。排窗纳蘋渚之清风。抬头望扶桑之出日。悠然而游。嚣然而乐。婆娑倘佯。无不自适。回看尘世之汩汩。是非之纷纷。都已忘筌。则仲实氏之游玆湖。岂不乐哉。虽然若使仲实氏僩然自足于今日之为。而又徒留情于湖海之胜。役志于景物之美。不为着力于观物察己。反求进益之功。则纵使玆湖之风物。绝胜于七百之洞庭三百之鉴湖。而仲实氏之所得于玆湖者。不过江海间渔翁钓叟之事耳。岂吾所谓遗尘遁世。而望于仲实氏者哉。必须刊落外慕。放下利欲。随分而安身。饫景而饱物。领略岭海之胜槩。恢吾胸臆。收拾湖山之爽气。养吾心性。时复闲阅经籍。静理训诂。所知益进。所得益富。使吾灵台。泂然洞然。而无一点之所累。则凡烟月渔钓之乐。无非有助于吾人。而虽处残溪断涧之间。亦足以有得。而况玆湖之胜。不下于洞庭,鉴湖者耶。夫然后可以无愧于斯行。而不负于玆湖矣。此吾所谓遗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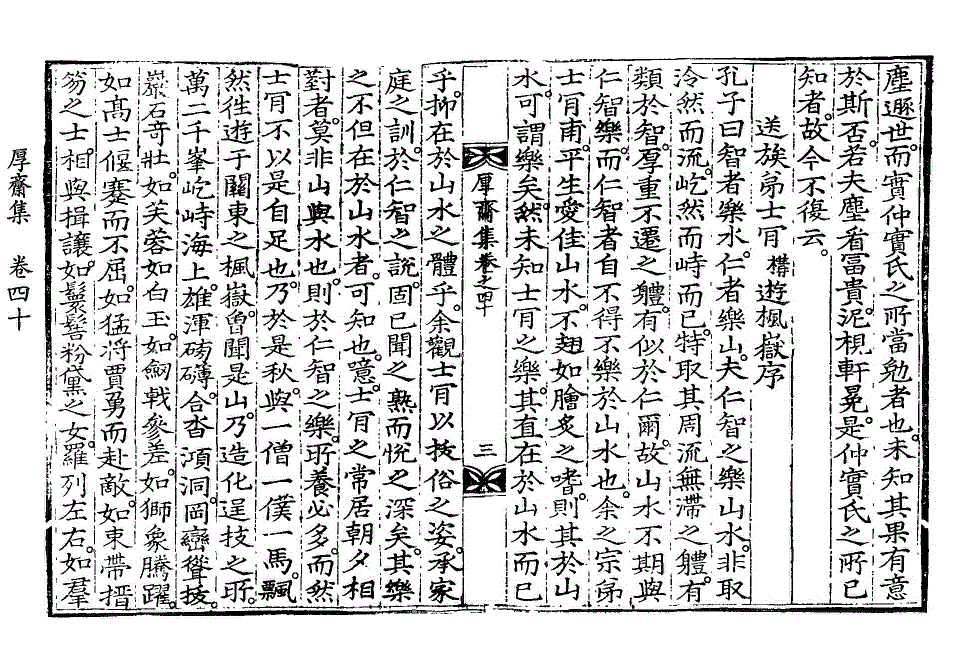 尘遁世。而实仲实氏之所当勉者也。未知其果有意于斯否。若夫尘看富贵。泥视轩冕。是仲实氏之所已知者。故今不复云。
尘遁世。而实仲实氏之所当勉者也。未知其果有意于斯否。若夫尘看富贵。泥视轩冕。是仲实氏之所已知者。故今不复云。送族弟士肯(构)游枫岳序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夫仁智之乐山水。非取泠然而流。屹然而峙而已。特取其周流无滞之体。有类于智。厚重不迁之体。有似于仁尔。故山水不期与仁智乐。而仁智者自不得不乐于山水也。余之宗弟士肯甫。平生爱佳山水。不翅如脍炙之嗜。则其于山水。可谓乐矣。然未知士肯之乐。其直在于山水而已乎。抑在于山水之体乎。余观士肯以拔俗之姿。承家庭之训。于仁智之说。固已闻之熟而悦之深矣。其乐之不但在于山水者。可知也。噫。士肯之常居朝夕相对者。莫非山与水也。则于仁智之乐。所养必多。而然士肯不以是自足也。乃于是秋。与一僧一仆一马。飘然往游于关东之枫岳。曾闻是山。乃造化逞技之所。万二千峰屹峙海上。雄浑磅礴。合沓澒洞。冈峦耸拔。岩石奇壮。如芙蓉如白玉。如剑戟参差。如狮象腾跃。如高士偃蹇而不屈。如猛将贾勇而赴敌。如束带搢笏之士。相与揖让。如鬟髻粉黛之女。罗列左右。如群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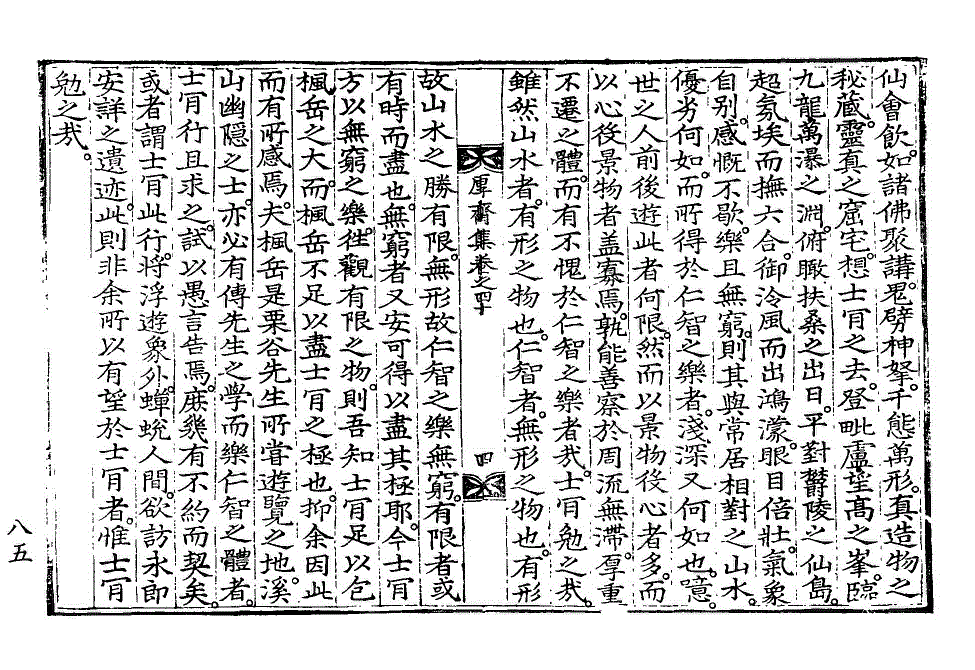 仙会饮。如诸佛聚讲。鬼劈神拿。千态万形。真造物之秘藏。灵真之窟宅。想士肯之去。登毗卢,望高之峰。临九龙,万瀑之渊。俯瞰扶桑之出日。平对郁陵之仙岛。超氛埃而抚六合。御泠风而出鸿濛。眼目倍壮。气象自别。感慨不歇。乐且无穷。则其与常居相对之山水。优劣何如。而所得于仁智之乐者。浅深又何如也。噫。世之人前后游此者何限。然而以景物役心者多。而以心役景物者盖寡焉。孰能善察于周流无滞。厚重不迁之体。而有不愧于仁智之乐者哉。士肯勉之哉。虽然山水者。有形之物也。仁智者。无形之物也。有形故山水之胜有限。无形故仁智之乐无穷。有限者或有时而尽也。无穷者又安可得以尽其极耶。今士肯方以无穷之乐。往观有限之物。则吾知士肯足以包枫岳之大。而枫岳不足以尽士肯之极也。抑余因此而有所感焉。夫枫岳是栗谷先生所尝游览之地。溪山幽隐之士。亦必有传先生之学而乐仁智之体者。士肯行且求之。试以愚言告焉。庶几有不约而契矣。或者谓士肯此行。将浮游象外。蝉蜕人间。欲访永郎安详之遗迹。此则非余所以有望于士肯者。惟士肯勉之哉。
仙会饮。如诸佛聚讲。鬼劈神拿。千态万形。真造物之秘藏。灵真之窟宅。想士肯之去。登毗卢,望高之峰。临九龙,万瀑之渊。俯瞰扶桑之出日。平对郁陵之仙岛。超氛埃而抚六合。御泠风而出鸿濛。眼目倍壮。气象自别。感慨不歇。乐且无穷。则其与常居相对之山水。优劣何如。而所得于仁智之乐者。浅深又何如也。噫。世之人前后游此者何限。然而以景物役心者多。而以心役景物者盖寡焉。孰能善察于周流无滞。厚重不迁之体。而有不愧于仁智之乐者哉。士肯勉之哉。虽然山水者。有形之物也。仁智者。无形之物也。有形故山水之胜有限。无形故仁智之乐无穷。有限者或有时而尽也。无穷者又安可得以尽其极耶。今士肯方以无穷之乐。往观有限之物。则吾知士肯足以包枫岳之大。而枫岳不足以尽士肯之极也。抑余因此而有所感焉。夫枫岳是栗谷先生所尝游览之地。溪山幽隐之士。亦必有传先生之学而乐仁智之体者。士肯行且求之。试以愚言告焉。庶几有不约而契矣。或者谓士肯此行。将浮游象外。蝉蜕人间。欲访永郎安详之遗迹。此则非余所以有望于士肯者。惟士肯勉之哉。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记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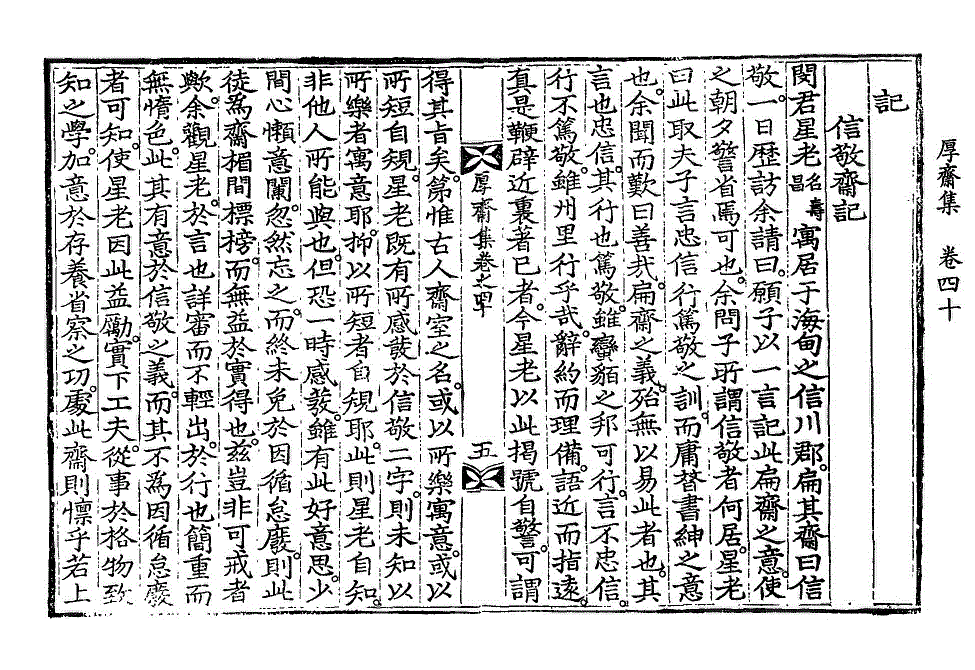 信敬斋记
信敬斋记闵君星老(名寿昌)寓居于海甸之信川郡。扁其斋曰信敬。一日历访余请曰。愿子以一言记此扁斋之意。使之朝夕警省焉可也。余问子所谓信敬者何居。星老曰此取夫子言忠信行笃敬之训。而庸替书绅之意也。余闻而叹曰善哉。扁斋之义。殆无以易此者也。其言也忠信。其行也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辞约而理备。语近而指远。真是鞭辟近里著己者。今星老以此揭号自警。可谓得其旨矣。第惟古人斋室之名。或以所乐寓意。或以所短自规。星老既有所感发于信敬二字。则未知以所乐者寓意耶。抑以所短者自规耶。此则星老自知。非他人所能与也。但恐一时感发。虽有此好意思。少间心懒意阑。忽然忘之。而终未免于因循怠废。则此徒为斋楣间标榜。而无益于实得也。玆岂非可戒者欤。余观星老。于言也详审而不轻出。于行也简重而无惰色。此其有意于信敬之义。而其不为因循怠废者可知。使星老因此益励。实下工夫。从事于格物致知之学。加意于存养省察之功。处此斋则懔乎若上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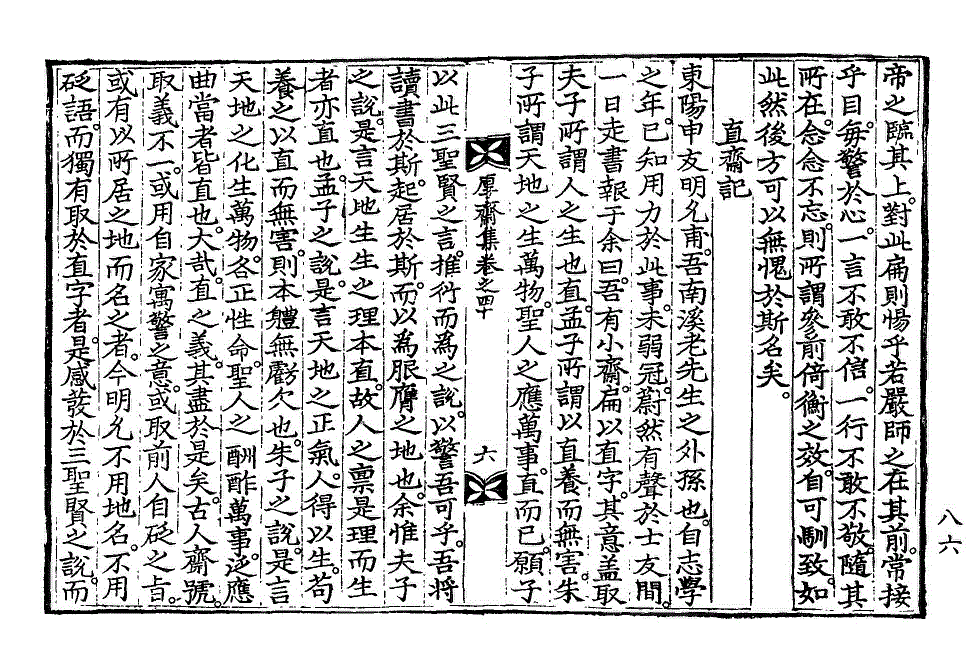 帝之临其上。对此扁则惕乎若严师之在其前。常接乎目。每警于心。一言不敢不信。一行不敢不敬。随其所在。念念不忘。则所谓参前倚衡之效。自可驯致。如此然后方可以无愧于斯名矣。
帝之临其上。对此扁则惕乎若严师之在其前。常接乎目。每警于心。一言不敢不信。一行不敢不敬。随其所在。念念不忘。则所谓参前倚衡之效。自可驯致。如此然后方可以无愧于斯名矣。直斋记
东阳申友明允甫。吾南溪老先生之外孙也。自志学之年。已知用力于此事。未弱冠。蔚然有声于士友间。一日走书报于余曰。吾有小斋。扁以直字。其意盖取夫子所谓人之生也直。孟子所谓以直养而无害。朱子所谓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应万事。直而已。愿子以此三圣贤之言。推衍而为之说。以警吾可乎。吾将读书于斯。起居于斯。而以为服膺之地也。余惟夫子之说。是言天地生生之理本直。故人之禀是理而生者亦直也。孟子之说。是言天地之正气。人得以生。苟养之以直而无害。则本体无亏欠也。朱子之说是言天地之化生万物。各正性命。圣人之酬酢万事。泛应曲当者皆直也。大哉。直之义。其尽于是矣。古人斋号。取义不一。或用自家寓警之意。或取前人自砭之旨。或有以所居之地而名之者。今明允不用地名。不用砭语。而独有取于直字者。是感发于三圣贤之说。而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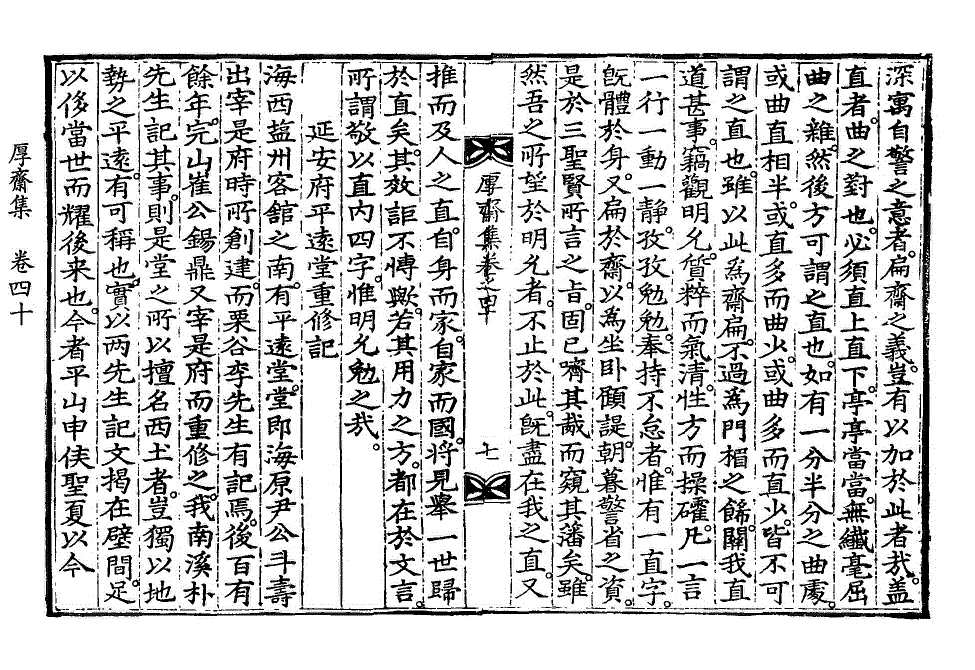 深寓自警之意者。扁斋之义。岂有以加于此者哉。盖直者。曲之对也。必须直上直下。亭亭当当。无纤毫屈曲之杂。然后方可谓之直也。如有一分半分之曲处。或曲直相半。或直多而曲少。或曲多而直少。皆不可谓之直也。虽以此为斋扁。不过为门楣之饰。关我直道甚事。窃观明允。质粹而气清。性方而操礭。凡一言一行一动一静。孜孜勉勉。奉持不怠者。惟有一直字。既体于身。又扁于斋。以为坐卧顾諟。朝暮警省之资。是于三圣贤所言之旨。固已哜其胾而窥其藩矣。虽然吾之所望于明允者。不止于此。既尽在我之直。又推而及人之直。自身而家。自家而国。将见举一世归于直矣。其效讵不博欤。若其用力之方。都在于文言。所谓敬以直内四字。惟明允勉之哉。
深寓自警之意者。扁斋之义。岂有以加于此者哉。盖直者。曲之对也。必须直上直下。亭亭当当。无纤毫屈曲之杂。然后方可谓之直也。如有一分半分之曲处。或曲直相半。或直多而曲少。或曲多而直少。皆不可谓之直也。虽以此为斋扁。不过为门楣之饰。关我直道甚事。窃观明允。质粹而气清。性方而操礭。凡一言一行一动一静。孜孜勉勉。奉持不怠者。惟有一直字。既体于身。又扁于斋。以为坐卧顾諟。朝暮警省之资。是于三圣贤所言之旨。固已哜其胾而窥其藩矣。虽然吾之所望于明允者。不止于此。既尽在我之直。又推而及人之直。自身而家。自家而国。将见举一世归于直矣。其效讵不博欤。若其用力之方。都在于文言。所谓敬以直内四字。惟明允勉之哉。延安府平远堂重修记
海西盐州客馆之南。有平远堂。堂即海原尹公斗寿出宰是府时所创建。而栗谷李先生有记焉。后百有馀年。完山崔公锡鼎又宰是府而重修之。我南溪朴先生记其事。则是堂之所以擅名西土者。岂独以地势之平远。有可称也。实以两先生记文揭在壁间。足以侈当世而耀后来也。今者平山申侯圣夏以今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7L 页
 上之某年某月。出守是土。距崔公时不过数十年。而堂又颓圮。侯以暇日登临于此。顾瞻咨嗟曰。是堂也经两公经纪。有两先生记文。而今将废而为蓬蒿之所。刍牧之场。岂不慨然可惜哉。遂以政通人和之馀。告于方伯。谋于邑民。鸠材聚工。不劳事集。凡栋梁甍桷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无不易而新之。其功视崔公尤有光焉。阅数月而功告讫。侯于是远走书嘱于干曰。愿子以一言为记。吾先师于此曾有记。则子何敢辞也。余悚然而作曰。侯之言是矣。顾余生长汉南。不见所谓平远堂者。且衰昏已甚。文字又拙。则今欲记其事而张大之。以承侯之勤托。其何可得也。虽然以两先生所为记者按之。庶几可据而言矣。栗谷先生之言曰是堂平临迥野。远挹江海。大池波光。遥岑积翠。萃于几席之间。又曰外境之胜。所以助养也。操存省察。乃养之本法也。务其助而忽其本。则亦非真养也。南溪先生之言曰以得名之义言之。其平则良田万顷。高原平隰。井井不紊。君子居之。可以存公正均和之心。其远则洪波千里。际天划地。荡荡无涯。君子居之。可以养弘大开通之知。又曰平者恕之符。远者明之致。噫。是堂
上之某年某月。出守是土。距崔公时不过数十年。而堂又颓圮。侯以暇日登临于此。顾瞻咨嗟曰。是堂也经两公经纪。有两先生记文。而今将废而为蓬蒿之所。刍牧之场。岂不慨然可惜哉。遂以政通人和之馀。告于方伯。谋于邑民。鸠材聚工。不劳事集。凡栋梁甍桷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无不易而新之。其功视崔公尤有光焉。阅数月而功告讫。侯于是远走书嘱于干曰。愿子以一言为记。吾先师于此曾有记。则子何敢辞也。余悚然而作曰。侯之言是矣。顾余生长汉南。不见所谓平远堂者。且衰昏已甚。文字又拙。则今欲记其事而张大之。以承侯之勤托。其何可得也。虽然以两先生所为记者按之。庶几可据而言矣。栗谷先生之言曰是堂平临迥野。远挹江海。大池波光。遥岑积翠。萃于几席之间。又曰外境之胜。所以助养也。操存省察。乃养之本法也。务其助而忽其本。则亦非真养也。南溪先生之言曰以得名之义言之。其平则良田万顷。高原平隰。井井不紊。君子居之。可以存公正均和之心。其远则洪波千里。际天划地。荡荡无涯。君子居之。可以养弘大开通之知。又曰平者恕之符。远者明之致。噫。是堂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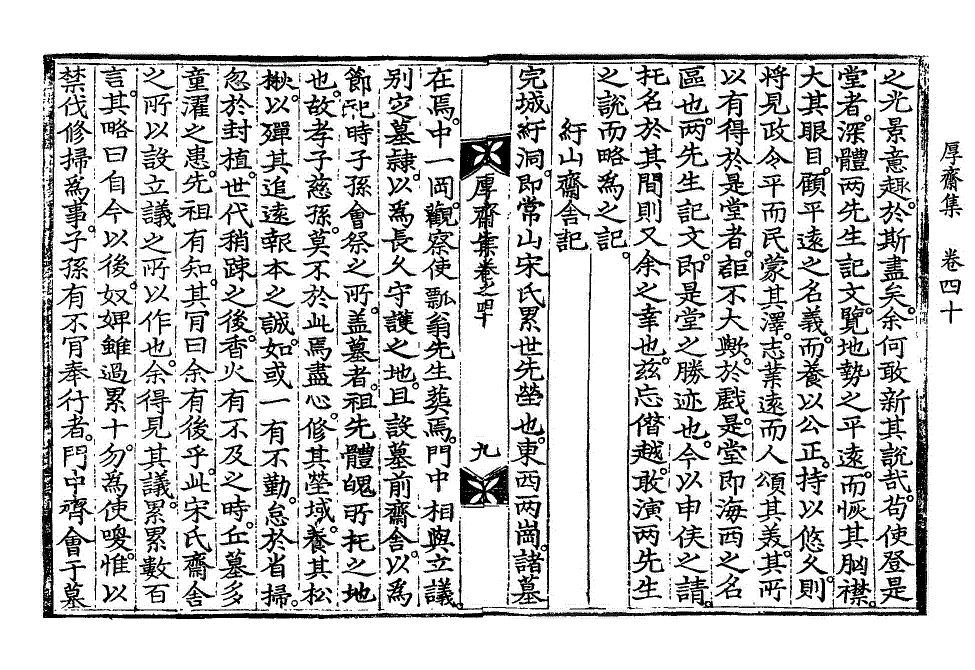 之光景意趣。于斯尽矣。余何敢新其说哉。苟使登是堂者。深体两先生记文。览地势之平远。而恢其胸襟。大其眼目。顾平远之名义。而养以公正。持以悠久。则将见政令平而民蒙其泽。志业远而人颂其美。其所以有得于是堂者。讵不大欤。于戏。是堂即海西之名区也。两先生记文。即是堂之胜迹也。今以申侯之请。托名于其间则又余之幸也。玆忘僭越。敢演两先生之说而略为之记。
之光景意趣。于斯尽矣。余何敢新其说哉。苟使登是堂者。深体两先生记文。览地势之平远。而恢其胸襟。大其眼目。顾平远之名义。而养以公正。持以悠久。则将见政令平而民蒙其泽。志业远而人颂其美。其所以有得于是堂者。讵不大欤。于戏。是堂即海西之名区也。两先生记文。即是堂之胜迹也。今以申侯之请。托名于其间则又余之幸也。玆忘僭越。敢演两先生之说而略为之记。纡山斋舍记
完城纡洞。即常山宋氏累世先茔也。东西两冈。诸墓在焉。中一冈。观察使瓢翁先生葬焉。门中相与立议。别定墓隶。以为长久守护之地。且设墓前斋舍。以为节祀时子孙会祭之所。盖墓者。祖先体魄所托之地也。故孝子慈孙。莫不于此焉尽心。修其茔域。养其松楸。以殚其追远报本之诚。如或一有不勤。怠于省扫。忽于封植。世代稍疏之后。香火有不及之时。丘墓多童濯之患。先祖有知。其肯曰余有后乎。此宋氏斋舍之所以设立议之所以作也。余得见其议。累累数百言。其略曰自今以后。奴婢虽过累十。勿为使唤。惟以禁伐修扫为事。子孙有不肯奉行者。门中齐会于墓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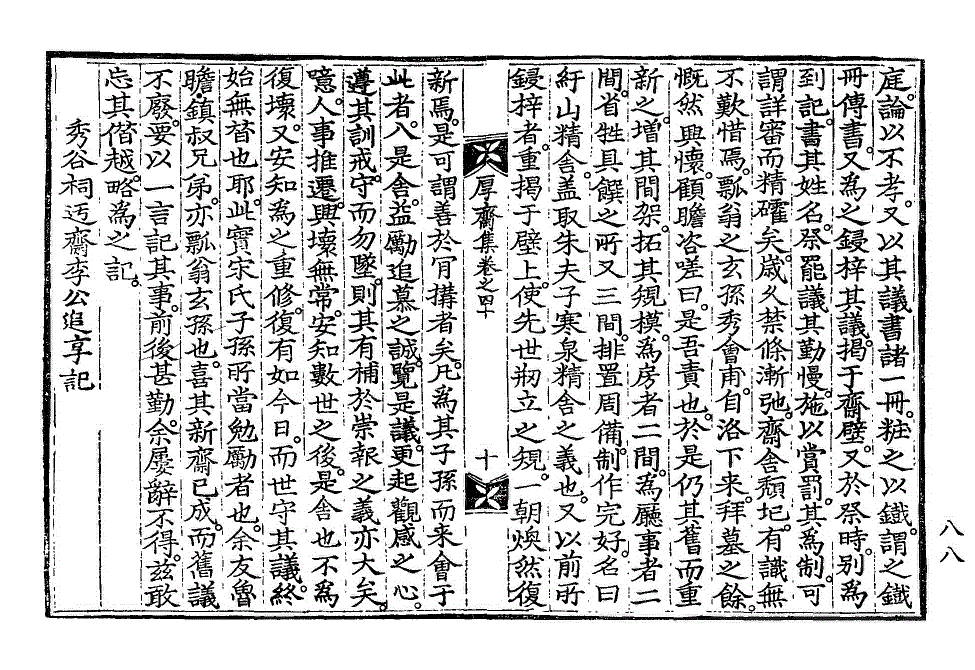 庭。论以不孝。又以其议书诸一册。妆之以铁。谓之铁册传书。又为之锓梓其议。揭于斋壁。又于祭时。别为到记。书其姓名。祭罢议其勤慢。施以赏罚。其为制。可谓详审而精礭矣。岁久禁条渐弛。斋舍颓圮。有识无不叹惜焉。瓢翁之玄孙秀会甫。自洛下来。拜墓之馀。慨然兴怀。顾瞻咨嗟曰。是吾责也。于是仍其旧而重新之。增其间架。拓其规模。为房者二间。为厅事者二间。省牲具馔之所又三间。排置周备。制作完好。名曰纡山精舍。盖取朱夫子寒泉精舍之义也。又以前所锓梓者。重揭于壁上。使先世刱立之规。一朝焕然复新焉。是可谓善于肯搆者矣。凡为其子孙而来会于此者。入是舍。益励追慕之诚。览是议。更起观感之心。遵其训戒。守而勿坠。则其有补于崇报之义亦大矣。噫。人事推迁。兴坏无常。安知数世之后。是舍也不为复坏。又安知为之重修。复有如今日。而世守其议。终始无替也耶。此实宋氏子孙所当勉励者也。余友鲁瞻,镇叔兄弟。亦瓢翁玄孙也。喜其新斋已成。而旧议不废。要以一言记其事。前后甚勤。余屡辞不得。玆敢忘其僭越。略为之记。
庭。论以不孝。又以其议书诸一册。妆之以铁。谓之铁册传书。又为之锓梓其议。揭于斋壁。又于祭时。别为到记。书其姓名。祭罢议其勤慢。施以赏罚。其为制。可谓详审而精礭矣。岁久禁条渐弛。斋舍颓圮。有识无不叹惜焉。瓢翁之玄孙秀会甫。自洛下来。拜墓之馀。慨然兴怀。顾瞻咨嗟曰。是吾责也。于是仍其旧而重新之。增其间架。拓其规模。为房者二间。为厅事者二间。省牲具馔之所又三间。排置周备。制作完好。名曰纡山精舍。盖取朱夫子寒泉精舍之义也。又以前所锓梓者。重揭于壁上。使先世刱立之规。一朝焕然复新焉。是可谓善于肯搆者矣。凡为其子孙而来会于此者。入是舍。益励追慕之诚。览是议。更起观感之心。遵其训戒。守而勿坠。则其有补于崇报之义亦大矣。噫。人事推迁。兴坏无常。安知数世之后。是舍也不为复坏。又安知为之重修。复有如今日。而世守其议。终始无替也耶。此实宋氏子孙所当勉励者也。余友鲁瞻,镇叔兄弟。亦瓢翁玄孙也。喜其新斋已成。而旧议不废。要以一言记其事。前后甚勤。余屡辞不得。玆敢忘其僭越。略为之记。秀谷祠迂斋李公追享记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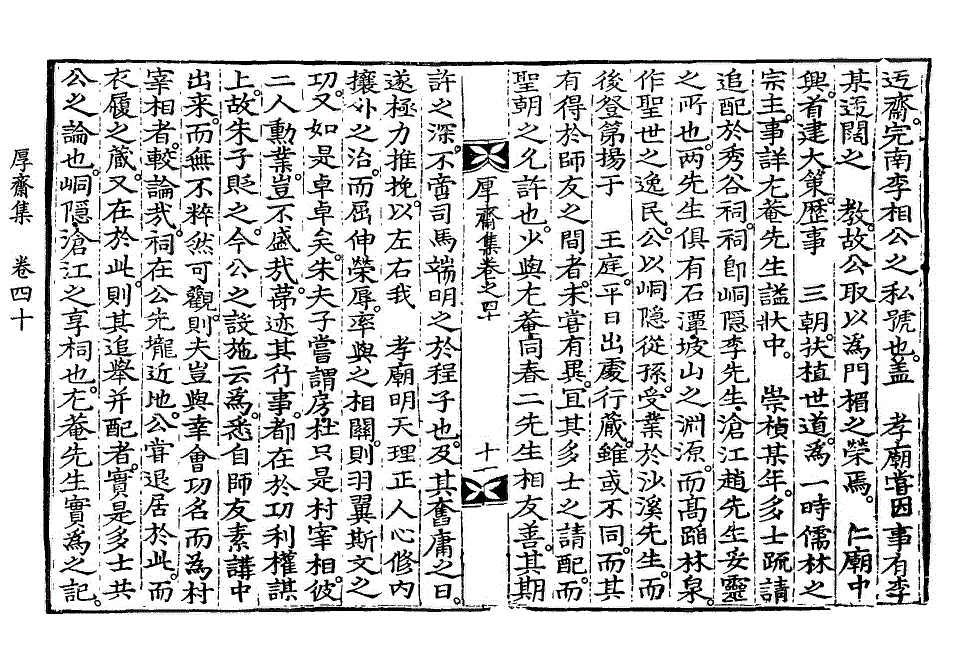 迂斋。完南李相公之私号也。盖 孝庙尝因事有李某迂阔之 教。故公取以为门楣之荣焉。 仁庙中兴。首建大策。历事 三朝。扶植世道。为一时儒林之宗主。事详尤庵先生谥状中。 崇祯某年。多士疏请追配于秀谷祠。祠即峒隐李先生,沧江赵先生妥灵之所也。两先生俱有石潭,坡山之渊源。而高蹈林泉。作圣世之逸民。公以峒隐从孙。受业于沙溪先生。而后登第扬于 王庭。平日出处行藏。虽或不同。而其有得于师友之间者。未尝有异。宜其多士之请配。而圣朝之允许也。少与尤庵,同春二先生相友善。其期许之深。不啻司马端明之于程子也。及其奋庸之日。遂极力推挽。以左右我 孝庙明天理正人心修内攘外之治。而屈伸荣辱。率与之相关。则羽翼斯文之功。又如是卓卓矣。朱夫子尝谓房,杜只是村宰相。彼二人勋业。岂不盛哉。第迹其行事。都在于功利权谋上。故朱子贬之。今公之设施云为。悉自师友素讲中出来。而无不粹然可观。则夫岂与幸会功名而为村宰相者。较论哉。祠在公先垄近地。公尝退居于此。而衣履之藏。又在于此。则其追举并配者。实是多士共公之论也。峒隐,沧江之享祠也。尤庵先生实为之记。
迂斋。完南李相公之私号也。盖 孝庙尝因事有李某迂阔之 教。故公取以为门楣之荣焉。 仁庙中兴。首建大策。历事 三朝。扶植世道。为一时儒林之宗主。事详尤庵先生谥状中。 崇祯某年。多士疏请追配于秀谷祠。祠即峒隐李先生,沧江赵先生妥灵之所也。两先生俱有石潭,坡山之渊源。而高蹈林泉。作圣世之逸民。公以峒隐从孙。受业于沙溪先生。而后登第扬于 王庭。平日出处行藏。虽或不同。而其有得于师友之间者。未尝有异。宜其多士之请配。而圣朝之允许也。少与尤庵,同春二先生相友善。其期许之深。不啻司马端明之于程子也。及其奋庸之日。遂极力推挽。以左右我 孝庙明天理正人心修内攘外之治。而屈伸荣辱。率与之相关。则羽翼斯文之功。又如是卓卓矣。朱夫子尝谓房,杜只是村宰相。彼二人勋业。岂不盛哉。第迹其行事。都在于功利权谋上。故朱子贬之。今公之设施云为。悉自师友素讲中出来。而无不粹然可观。则夫岂与幸会功名而为村宰相者。较论哉。祠在公先垄近地。公尝退居于此。而衣履之藏。又在于此。则其追举并配者。实是多士共公之论也。峒隐,沧江之享祠也。尤庵先生实为之记。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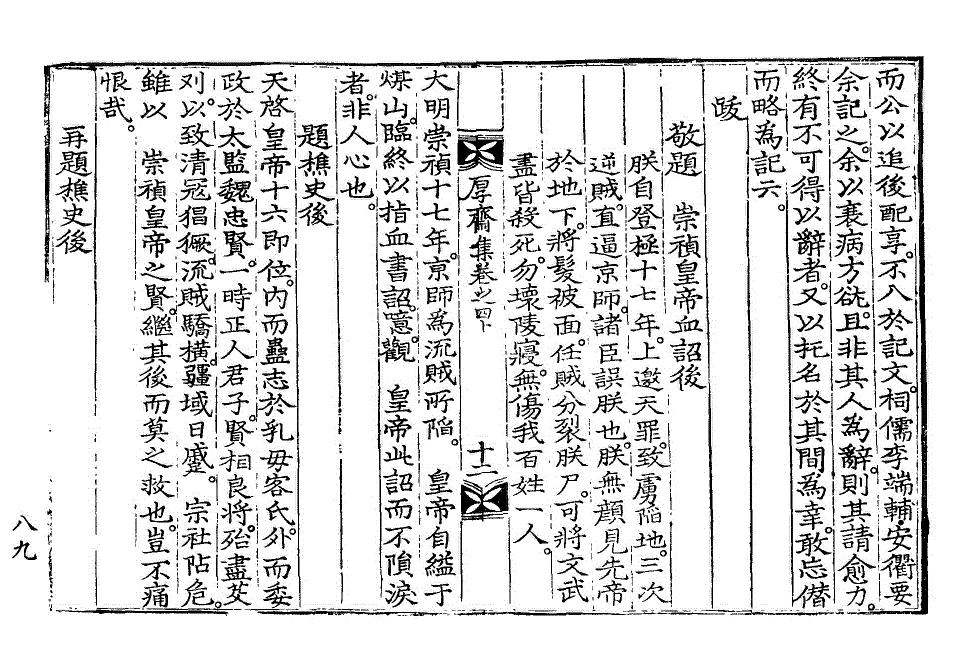 而公以追后配享。不入于记文。祠儒李端辅,安衢要余记之。余以衰病方谻。且非其人为辞。则其请愈力。终有不可得以辞者。又以托名于其间为幸。敢忘僭而略为记云。
而公以追后配享。不入于记文。祠儒李端辅,安衢要余记之。余以衰病方谻。且非其人为辞。则其请愈力。终有不可得以辞者。又以托名于其间为幸。敢忘僭而略为记云。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跋
敬题 崇祯皇帝血诏后
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被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无伤我百姓一人。
大明崇祯十七年。京师为流贼所陷。 皇帝自缢于煤山。临终以指血书诏。噫。观 皇帝此诏而不陨泪者。非人心也。
题樵史后
天启皇帝十六即位。内而蛊志于乳母客氏。外而委政于太监魏忠贤。一时正人君子。贤相良将。殆尽芟刈。以致清寇猖獗。流贼骄横。疆域日蹙。 宗社阽危。虽以 崇祯皇帝之贤。继其后而莫之救也。岂不痛恨哉。
再题樵史后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0H 页
 余观樵史。至魏忠贤事。未尝不扼腕而愤叹也。其诬弄幼主。戕杀忠良。甚于汉之曹节。其专擅权势。病民害国。甚于秦之赵高。至若生祠之建。九千岁之呼。又赵高,曹节之所未有也。噫。一赵高足以覆秦之宗社。一曹节足以亡汉之大下。况忠贤兼高节之恶。而又有甚焉者。则 明虽欲不亡。得乎。
余观樵史。至魏忠贤事。未尝不扼腕而愤叹也。其诬弄幼主。戕杀忠良。甚于汉之曹节。其专擅权势。病民害国。甚于秦之赵高。至若生祠之建。九千岁之呼。又赵高,曹节之所未有也。噫。一赵高足以覆秦之宗社。一曹节足以亡汉之大下。况忠贤兼高节之恶。而又有甚焉者。则 明虽欲不亡。得乎。题玄石先生跋履素斋心性情图后
干间得履素斋李公所著心性情图若诗说于公之裔以鼎氏藏。亲笔也。谨献于吾先生。因请曰愿有以跋其后也。既而先生为之妆䌙补缀。且白其下。书图说之同异得失以归之。干伏擎读之。其所以发明图意。更无遗欠。此岂特幸公之子孙。抑为后学赐大矣。谨按此图。盖有前贤所未发者。若非见道之明。勇往直前。亡少疑晦。其何能及此。然而退老于此。有道学精微未可轻拟之语。何也。此则吾先生之说。论之已尽矣。第以妄见中间一图。以虚为体。以灵为用。而知觉又居灵后。此虚灵知觉。分为三截。情在于上。几在于下。而意又居其间。此情意几判为三件。慎独自是省察事也。而不同其置。恻隐辞让是非羞恶。自是情也。而又别其位。如四端理动。七情气动之说。并与旧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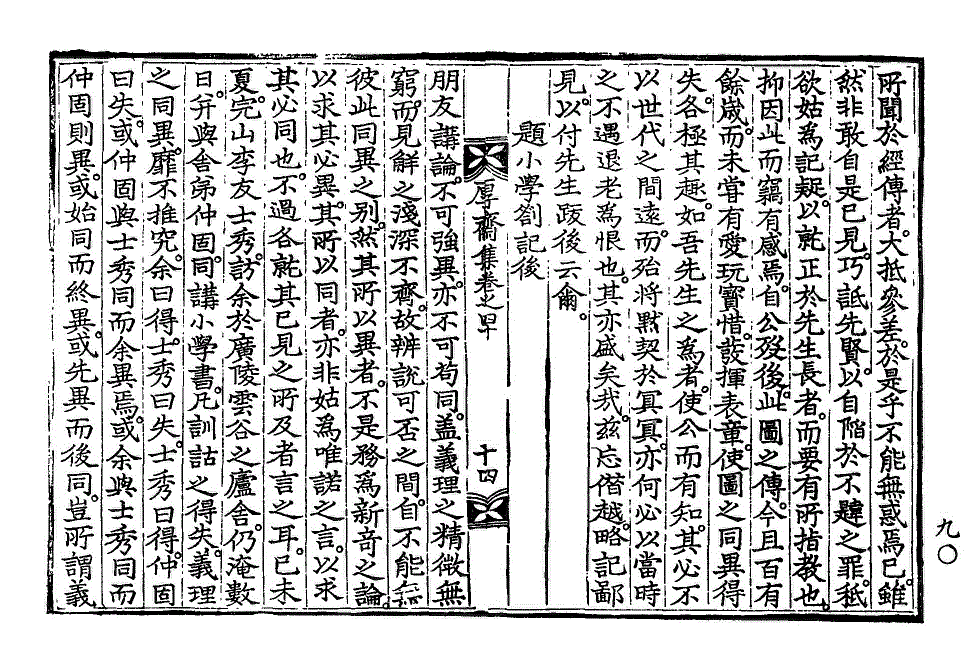 所闻于经传者。大抵参差。于是乎不能无惑焉已。虽然非敢自是己见。巧诋先贤。以自陷于不韪之罪。秪欲姑为记疑。以就正于先生长者。而要有所指教也。抑因此而窃有感焉。自公殁后。此图之传。今且百有馀岁。而未尝有爱玩宝惜。发挥表章。使图之同异得失。各极其趣。如吾先生之为者。使公而有知。其必不以世代之间远。而殆将默契于冥冥。亦何必以当时之不遇退老为恨也。其亦盛矣哉。玆忘僭越。略记鄙见。以付先生跋后云尔。
所闻于经传者。大抵参差。于是乎不能无惑焉已。虽然非敢自是己见。巧诋先贤。以自陷于不韪之罪。秪欲姑为记疑。以就正于先生长者。而要有所指教也。抑因此而窃有感焉。自公殁后。此图之传。今且百有馀岁。而未尝有爱玩宝惜。发挥表章。使图之同异得失。各极其趣。如吾先生之为者。使公而有知。其必不以世代之间远。而殆将默契于冥冥。亦何必以当时之不遇退老为恨也。其亦盛矣哉。玆忘僭越。略记鄙见。以付先生跋后云尔。题小学劄记后
朋友讲论。不可强异。亦不可苟同。盖义理之精微无穷。而见解之浅深不齐。故辨说可否之间。自不能无彼此同异之别。然其所以异者。不是务为新奇之论。以求其必异。其所以同者。亦非姑为唯诺之言。以求其必同也。不过各就其己见之所及者言之耳。己未夏。完山李友士秀。访余于广陵云谷之庐舍。仍淹数日。并与舍弟仲固。同讲小学书。凡训诂之得失。义理之同异。靡不推究。余曰得。士秀曰失。士秀曰得。仲固曰失。或仲固与士秀同而余异焉。或余与士秀同而仲固则异。或始同而终异。或先异而后同。岂所谓义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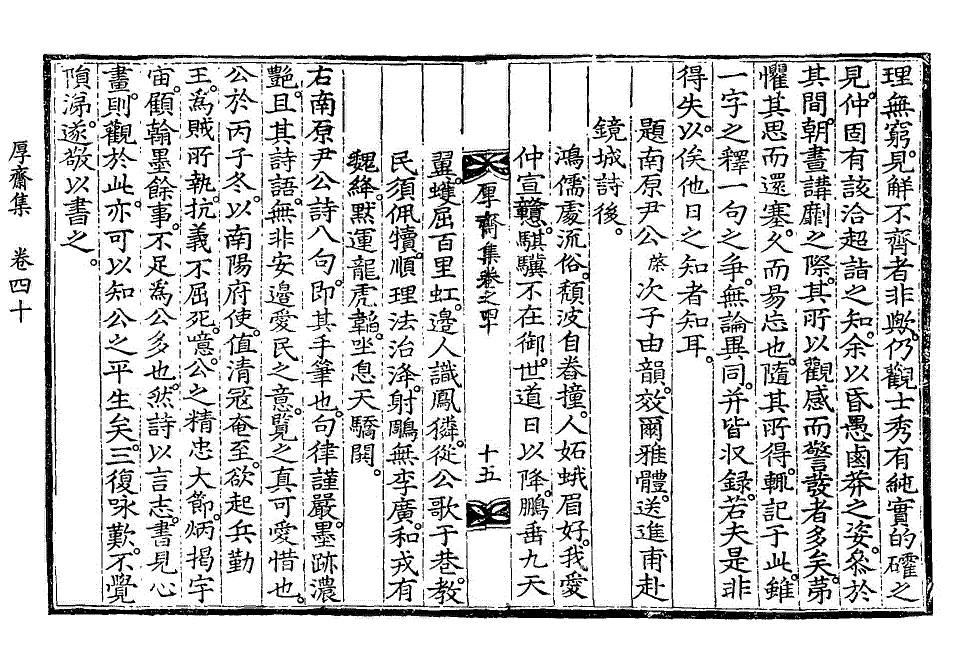 理无穷。见解不齐者非欤。仍观士秀有纯实的礭之见。仲固有该洽超诣之知。余以昏愚卤莽之姿。参于其间。朝昼讲劘之际。其所以观感而警发者多矣。第惧其思而还塞。久而易忘也。随其所得。辄记于此。虽一字之释一句之争。无论异同。并皆收录。若夫是非得失。以俟他日之知者知耳。
理无穷。见解不齐者非欤。仍观士秀有纯实的礭之见。仲固有该洽超诣之知。余以昏愚卤莽之姿。参于其间。朝昼讲劘之际。其所以观感而警发者多矣。第惧其思而还塞。久而易忘也。随其所得。辄记于此。虽一字之释一句之争。无论异同。并皆收录。若夫是非得失。以俟他日之知者知耳。题南原尹公(棨)次子由韵。效尔雅体。送进甫赴镜城诗后。
鸿儒处流俗。颓波自舂撞。人妒蛾眉好。我爱仲宣戆。骐骥不在御。世道日以降。鹏垂九天翼。蠖屈百里虹。边人识凤麟。从公歌于巷。教民须佩犊。顺理法治洚。射雕无李广。和戎有魏绛。默运龙虎韬。坐息天骄鬨。
右南原尹公诗八句。即其手笔也。句律谨严。墨迹浓艳。且其诗语。无非安边爱民之意。览之真可爱惜也。公于丙子冬。以南阳府使。值清寇奄至。欲起兵勤 王。为贼所执。抗义不屈死。噫。公之精忠大节。炳揭宇宙。顾翰墨馀事。不足为公多也。然诗以言志。书见心画。则观于此。亦可以知公之平生矣。三复咏叹。不觉陨涕。遂敬以书之。
题退溪先生书敬斋箴后
曾观金河西送退溪先生诗曰。夫子岭之秀。李杜文章王赵笔。干窃尝以王赵笔三字。为一时过褒之词矣。近得先生亲笔于聘君家。乃先生书敬斋箴者也。太半散逸。只馀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勿贰以二。勿参以三四句十六字。字画精研。墨华浓郁。所谓王赵笔者。果不诬矣。然其法度缜密。气象谨严。则又非寻常笔家之流也。程夫子尝曰某作字时甚敬。今观先生之笔。其亦有得于敬字也夫。将十袭谨藏。以为传家之宝云。后学清风金干敬书。
题安平大君亲笔后
世传大君初于书甚拙。尝行过路。见卖油者在高楼上。以盆注油于楼下小瓶中。大君见而奇之曰。此必有多少工夫。遂归家发愤习字。几于忘寝与飧。后果入于精妙之域。华使尝见而称之曰。此东方之孟頫也。噫。书法小技也。尚能如此用工。方有所成就。况又有大于书法者耶。世之学者。庶亦鉴于玆而知所勉哉。
题花潭先生集后
花潭徐先生。我 仁明朝大儒也。自少晦迹山林。探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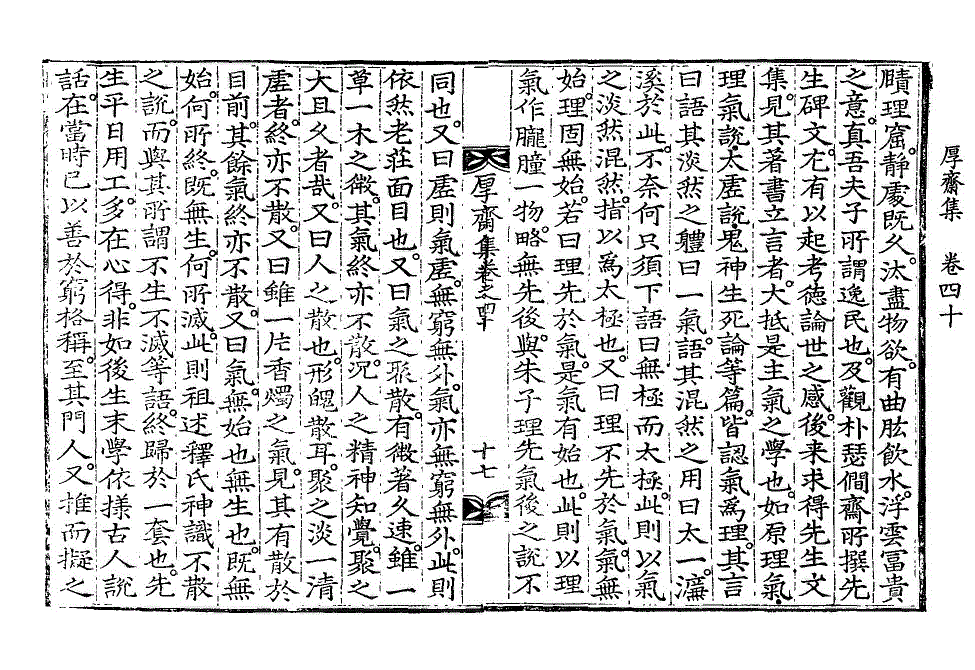 赜理窟。静处既久。汰尽物欲。有曲肱饮水。浮云富贵之意。真吾夫子所谓逸民也。及观朴瑟僩斋所撰先生碑文。尤有以起考德论世之感。后来求得先生文集。见其著书立言者。大抵是主气之学也。如原理气,理气说,太虚说,鬼神生死论等篇。皆认气为理。其言曰语其淡然之体曰一气。语其混然之用曰太一。濂溪于此。不奈何只须下语曰无极而太极。此则以气之淡然混然。指以为太极也。又曰理不先于气。气无始。理固无始。若曰理先于气。是气有始也。此则以理气作胧朣一物。略无先后。与朱子理先气后之说不同也。又曰虚则气虚。无穷无外。气亦无穷无外。此则依然老庄面目也。又曰气之聚散。有微著久速。虽一草一木之微。其气终亦不散。况人之精神知觉。聚之大且久者哉。又曰人之散也。形魄散耳。聚之淡一清虚者。终亦不散。又曰虽一片香烛之气。见其有散于目前。其馀气终亦不散。又曰气。无始也无生也。既无始。何所终。既无生。何所灭。此则祖述释氏神识不散之说。而与其所谓不生不灭等语。终归于一套也。先生平日用工。多在心得。非如后生末学依样古人说话。在当时已以善于穷格称。至其门人。又推而拟之
赜理窟。静处既久。汰尽物欲。有曲肱饮水。浮云富贵之意。真吾夫子所谓逸民也。及观朴瑟僩斋所撰先生碑文。尤有以起考德论世之感。后来求得先生文集。见其著书立言者。大抵是主气之学也。如原理气,理气说,太虚说,鬼神生死论等篇。皆认气为理。其言曰语其淡然之体曰一气。语其混然之用曰太一。濂溪于此。不奈何只须下语曰无极而太极。此则以气之淡然混然。指以为太极也。又曰理不先于气。气无始。理固无始。若曰理先于气。是气有始也。此则以理气作胧朣一物。略无先后。与朱子理先气后之说不同也。又曰虚则气虚。无穷无外。气亦无穷无外。此则依然老庄面目也。又曰气之聚散。有微著久速。虽一草一木之微。其气终亦不散。况人之精神知觉。聚之大且久者哉。又曰人之散也。形魄散耳。聚之淡一清虚者。终亦不散。又曰虽一片香烛之气。见其有散于目前。其馀气终亦不散。又曰气。无始也无生也。既无始。何所终。既无生。何所灭。此则祖述释氏神识不散之说。而与其所谓不生不灭等语。终归于一套也。先生平日用工。多在心得。非如后生末学依样古人说话。在当时已以善于穷格称。至其门人。又推而拟之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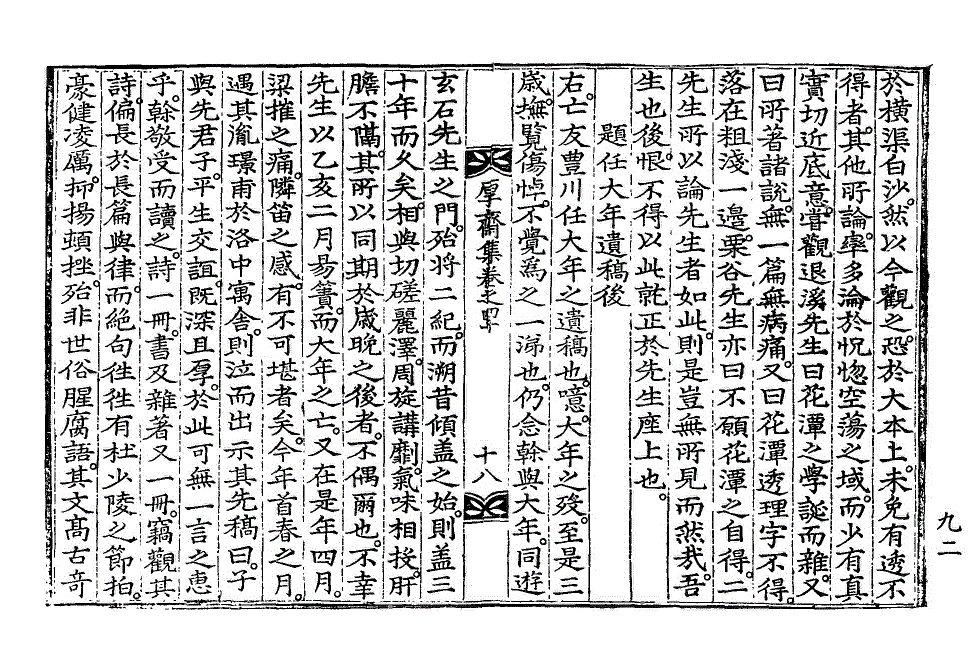 于横渠白沙。然以今观之。恐于大本上。未免有透不得者。其他所论。率多沦于恍惚空荡之域。而少有真实切近底意。尝观退溪先生曰花潭之学诞而杂。又曰所著诸说。无一篇无病痛。又曰花潭透理字不得。落在粗浅一边。栗谷先生亦曰不愿花潭之自得。二先生所以论先生者如此。则是岂无所见而然哉。吾生也后。恨不得以此就正于先生座上也。
于横渠白沙。然以今观之。恐于大本上。未免有透不得者。其他所论。率多沦于恍惚空荡之域。而少有真实切近底意。尝观退溪先生曰花潭之学诞而杂。又曰所著诸说。无一篇无病痛。又曰花潭透理字不得。落在粗浅一边。栗谷先生亦曰不愿花潭之自得。二先生所以论先生者如此。则是岂无所见而然哉。吾生也后。恨不得以此就正于先生座上也。题任大年遗稿后
右。亡友丰川任大年之遗稿也。噫。大年之殁。至是三岁。抚览伤悼。不觉为之一涕也。仍念干与大年。同游玄石先生之门。殆将二纪。而溯昔倾盖之始。则盖三十年而久矣。相与切磋丽泽。周旋讲劘。气味相投。肝胆不隔。其所以同期于岁晚之后者。不偶尔也。不幸先生以乙亥二月易箦。而大年之亡。又在是年四月。梁摧之痛。邻笛之感。有不可堪者矣。今年首春之月。遇其胤璟甫于洛中寓舍。则泣而出示其先稿曰。子与先君子。平生交谊。既深且厚。于此可无一言之惠乎。干敬受而读之。诗一册。书及杂著又一册。窃观其诗。偏长于长篇与律。而绝句往往有杜少陵之节拍。豪健凌厉。抑扬顿挫。殆非世俗腥腐语。其文高古奇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3H 页
 崛。深厚严密。汪洋大肆。有堂堂丈夫气。而无雕刻纂组安排费力之态。其间所论帝王得失。人物优劣。兵田之制。常变之礼者。其命意正。立言粹。出入经史。罗络古今。爬疏剔抉。明白宏阔。皆可实用。而不为空言。至其与人书札。又丁宁恳挚。策励劝勉。不但问寒暄通辞命而已。虽然此犹未足以尽大年之蕴也。如知智解,心说,五行生成说,小学劄记说,论近思录次序及辨李君辅正心章说,金士直太极往复书等说。皆研精覃思。毫分缕析。引物连类。取彼明此。俱得折衷。各极其趣。幽阐疑释。焕然若指掌。此非有得于平日师友之讲。心得之妙。而积厚蓄博者。何能有此哉。于此可以见渊源之正。学术之精。而其文章才识。悉本诸此耳。览是藁者。又不可不知此意也。俯仰存没。为之慨然。而且于其胤之请。有不可孤者。玆敢忘其僭率。谨识于后以归之。
崛。深厚严密。汪洋大肆。有堂堂丈夫气。而无雕刻纂组安排费力之态。其间所论帝王得失。人物优劣。兵田之制。常变之礼者。其命意正。立言粹。出入经史。罗络古今。爬疏剔抉。明白宏阔。皆可实用。而不为空言。至其与人书札。又丁宁恳挚。策励劝勉。不但问寒暄通辞命而已。虽然此犹未足以尽大年之蕴也。如知智解,心说,五行生成说,小学劄记说,论近思录次序及辨李君辅正心章说,金士直太极往复书等说。皆研精覃思。毫分缕析。引物连类。取彼明此。俱得折衷。各极其趣。幽阐疑释。焕然若指掌。此非有得于平日师友之讲。心得之妙。而积厚蓄博者。何能有此哉。于此可以见渊源之正。学术之精。而其文章才识。悉本诸此耳。览是藁者。又不可不知此意也。俯仰存没。为之慨然。而且于其胤之请。有不可孤者。玆敢忘其僭率。谨识于后以归之。题闵彦晖(以升)中庸图后
彦晖此图。较之平日诸作。颇似精细。然犹疏阙差谬处甚多。今以其一二可疑者言之。中庸第一章首三言。为一篇之纲领总要。故自此以下。篇中所论许多义理。皆自三言中推出说去。作图者当以此三言为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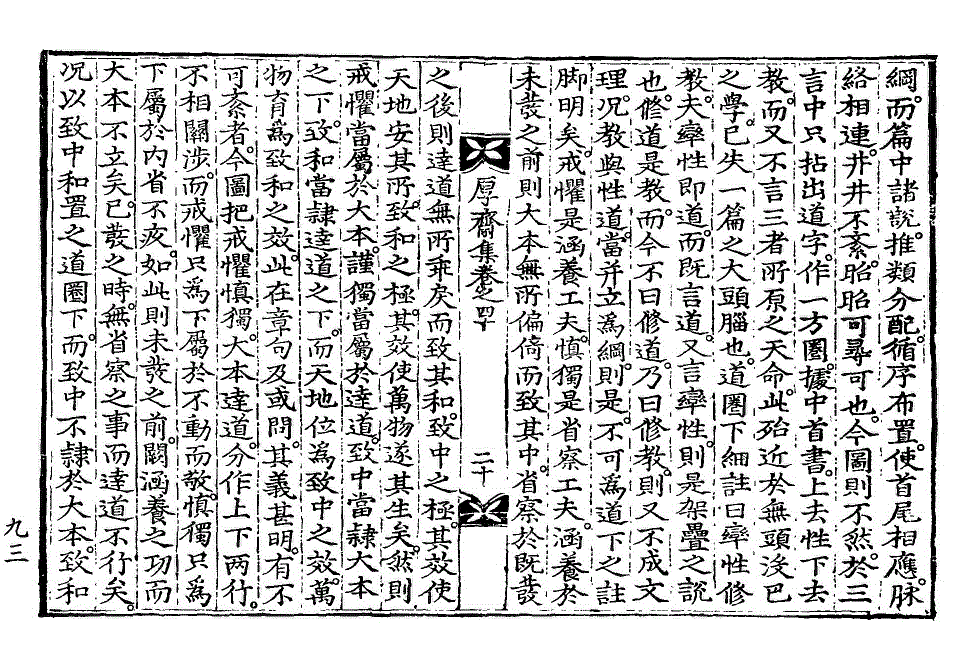 纲。而篇中诸说。推类分配。循序布置。使首尾相应。脉络相连。井井不紊。昭昭可寻可也。今图则不然。于三言中只拈出道字。作一方圈。据中首书。上去性下去教。而又不言三者所原之天命。此殆近于无头没巴之学。已失一篇之大头脑也。道圈下细注曰率性修教。夫率性即道。而既言道。又言率性。则是架叠之说也。修道是教。而今不曰修道。乃曰修教。则又不成文理。况教与性道。当并立为纲。则是。不可为道下之注脚明矣。戒惧是涵养工夫。慎独是省察工夫。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大本无所偏倚而致其中。省察于既发之后则达道无所乖戾而致其和。致中之极。其效使天地安其所。致和之极。其效使万物遂其生矣。然则戒惧当属于大本。谨独当属于达道。致中当隶大本之下。致和当隶达道之下。而天地位为致中之效。万物育为致和之效。此在章句及或问。其义甚明。有不可紊者。今图把戒惧慎独。大本达道。分作上下两行。不相关涉。而戒惧只为下属于不动而敬。慎独只为下属于内省不疚。如此则未发之前。阙涵养之功而大本不立矣。已发之时。无省察之事而达道不行矣。况以致中和置之道圈下。而致中不隶于大本。致和
纲。而篇中诸说。推类分配。循序布置。使首尾相应。脉络相连。井井不紊。昭昭可寻可也。今图则不然。于三言中只拈出道字。作一方圈。据中首书。上去性下去教。而又不言三者所原之天命。此殆近于无头没巴之学。已失一篇之大头脑也。道圈下细注曰率性修教。夫率性即道。而既言道。又言率性。则是架叠之说也。修道是教。而今不曰修道。乃曰修教。则又不成文理。况教与性道。当并立为纲。则是。不可为道下之注脚明矣。戒惧是涵养工夫。慎独是省察工夫。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大本无所偏倚而致其中。省察于既发之后则达道无所乖戾而致其和。致中之极。其效使天地安其所。致和之极。其效使万物遂其生矣。然则戒惧当属于大本。谨独当属于达道。致中当隶大本之下。致和当隶达道之下。而天地位为致中之效。万物育为致和之效。此在章句及或问。其义甚明。有不可紊者。今图把戒惧慎独。大本达道。分作上下两行。不相关涉。而戒惧只为下属于不动而敬。慎独只为下属于内省不疚。如此则未发之前。阙涵养之功而大本不立矣。已发之时。无省察之事而达道不行矣。况以致中和置之道圈下。而致中不隶于大本。致和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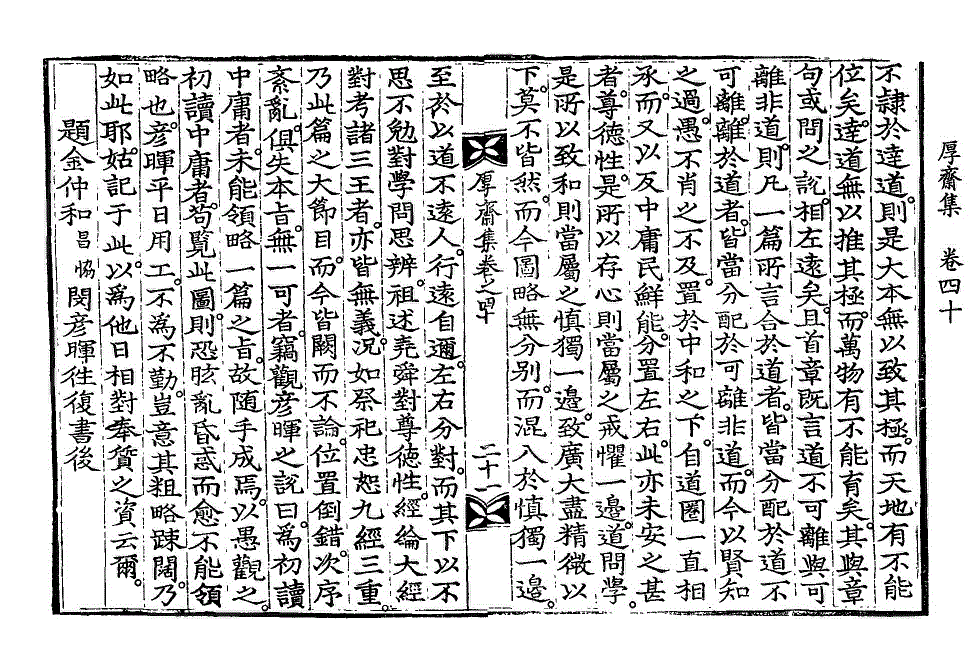 不隶于达道。则是大本无以致其极。而天地有不能位矣。达道无以推其极。而万物有不能育矣。其与章句或问之说。相左远矣。且首章既言道不可离与可离非道。则凡一篇所言合于道者。皆当分配于道不可离。离于道者。皆当分配于可离非道。而今以贤知之过。愚不肖之不及。置于中和之下。自道圈一直相承。而又以反中庸民鲜能。分置左右。此亦未安之甚者。尊德性。是所以存心则当属之戒惧一边。道问学。是所以致和则当属之慎独一边。致广大尽精微以下。莫不皆然。而今图略无分别。而混入于慎独一边。至于以道不远人。行远自迩。左右分对。而其下以不思不勉对学问思辨。祖述尧舜对尊德性。经纶大经对考诸三王者。亦皆无义。况如祭祀忠恕九经三重。乃此篇之大节目。而今皆阙而不论。位置倒错。次序紊乱。俱失本旨。无一可者。窃观彦晖之说曰。为初读中庸者。未能领略一篇之旨。故随手成焉。以愚观之。初读中庸者。苟览此图。则恐眩乱昏惑而愈不能领略也。彦晖平日用工。不为不勤。岂意其粗略疏阔。乃如此耶。姑记于此。以为他日相对奉质之资云尔。
不隶于达道。则是大本无以致其极。而天地有不能位矣。达道无以推其极。而万物有不能育矣。其与章句或问之说。相左远矣。且首章既言道不可离与可离非道。则凡一篇所言合于道者。皆当分配于道不可离。离于道者。皆当分配于可离非道。而今以贤知之过。愚不肖之不及。置于中和之下。自道圈一直相承。而又以反中庸民鲜能。分置左右。此亦未安之甚者。尊德性。是所以存心则当属之戒惧一边。道问学。是所以致和则当属之慎独一边。致广大尽精微以下。莫不皆然。而今图略无分别。而混入于慎独一边。至于以道不远人。行远自迩。左右分对。而其下以不思不勉对学问思辨。祖述尧舜对尊德性。经纶大经对考诸三王者。亦皆无义。况如祭祀忠恕九经三重。乃此篇之大节目。而今皆阙而不论。位置倒错。次序紊乱。俱失本旨。无一可者。窃观彦晖之说曰。为初读中庸者。未能领略一篇之旨。故随手成焉。以愚观之。初读中庸者。苟览此图。则恐眩乱昏惑而愈不能领略也。彦晖平日用工。不为不勤。岂意其粗略疏阔。乃如此耶。姑记于此。以为他日相对奉质之资云尔。题金仲和(昌协)、闵彦晖往复书后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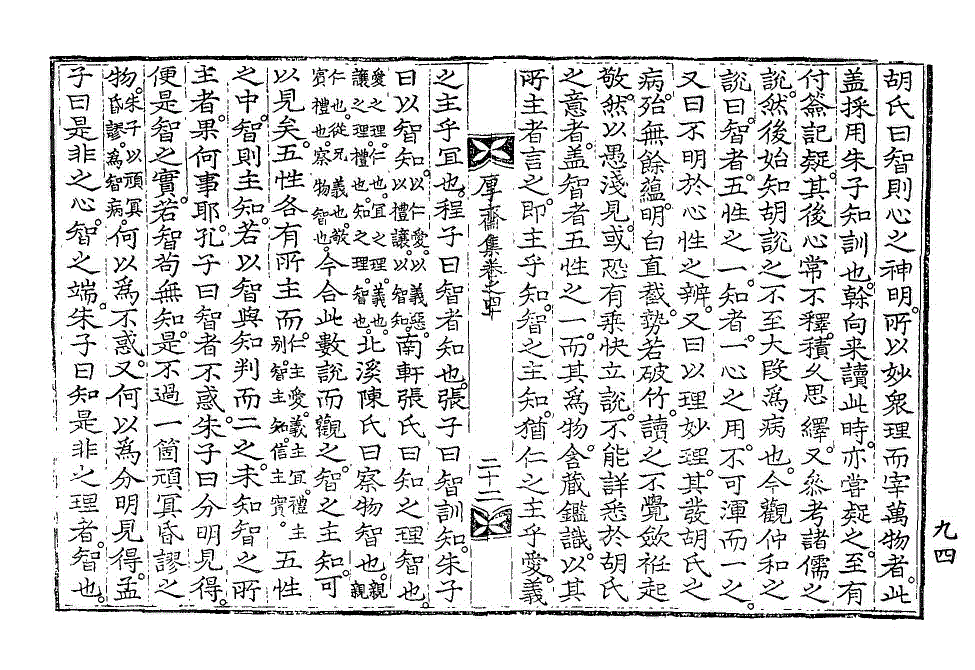 胡氏曰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此盖采用朱子知训也。干向来读此时。亦尝疑之。至有付签记疑。其后心常不释。积久思绎。又参考诸儒之说。然后始知胡说之不至大段为病也。今观仲和之说曰。智者。五性之一。知者。一心之用。不可浑而一之。又曰不明于心性之辨。又曰以理妙理。其发胡氏之病。殆无馀蕴。明白直截。势若破竹。读之不觉敛衽起敬。然以愚浅见。或恐有乘快立说。不能详悉于胡氏之意者。盖智者五性之一。而其为物。含藏鉴识。以其所主者言之。即主乎知。智之主知。犹仁之主乎爱。义之主乎宜也。程子曰智者知也。张子曰智训知。朱子曰以智知。(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南轩张氏曰知之理智也。(爱之理。仁也。宜之理。义也。让之理。礼也。知之理。智也。)北溪陈氏曰察物智也。(亲亲仁也。从兄义也。敬宾礼也。察物智也。)今合此数说而观之。智之主知。可以见矣。五性各有所主而。(仁主爱。义主宜。礼主别。智主知。信主实。)五性之中。智则主知。若以智与知判而二之。未知智之所主者。果何事耶。孔子曰智者不惑。朱子曰分明见得。便是智之实。若智苟无知。是不过一个顽冥昏谬之物。(朱子以顽冥昏谬。为智病。)何以为不惑。又何以为分明见得。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朱子曰知是非之理者。智也。
胡氏曰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此盖采用朱子知训也。干向来读此时。亦尝疑之。至有付签记疑。其后心常不释。积久思绎。又参考诸儒之说。然后始知胡说之不至大段为病也。今观仲和之说曰。智者。五性之一。知者。一心之用。不可浑而一之。又曰不明于心性之辨。又曰以理妙理。其发胡氏之病。殆无馀蕴。明白直截。势若破竹。读之不觉敛衽起敬。然以愚浅见。或恐有乘快立说。不能详悉于胡氏之意者。盖智者五性之一。而其为物。含藏鉴识。以其所主者言之。即主乎知。智之主知。犹仁之主乎爱。义之主乎宜也。程子曰智者知也。张子曰智训知。朱子曰以智知。(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南轩张氏曰知之理智也。(爱之理。仁也。宜之理。义也。让之理。礼也。知之理。智也。)北溪陈氏曰察物智也。(亲亲仁也。从兄义也。敬宾礼也。察物智也。)今合此数说而观之。智之主知。可以见矣。五性各有所主而。(仁主爱。义主宜。礼主别。智主知。信主实。)五性之中。智则主知。若以智与知判而二之。未知智之所主者。果何事耶。孔子曰智者不惑。朱子曰分明见得。便是智之实。若智苟无知。是不过一个顽冥昏谬之物。(朱子以顽冥昏谬。为智病。)何以为不惑。又何以为分明见得。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朱子曰知是非之理者。智也。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5H 页
 又曰知觉。乃智之事。若以知谓不管于智。而专为心之用则何以曰智之端。又何以曰知是非者智也。而至于所谓智之事。尤为明白的当。无少可疑也。夫智自是知底物事。凡有所知。皆主于智。故朱子以别忠佞分善恶。辨义理公私。俱谓之智。然则凡天下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有万不同。纷纭错综。不可究诘。而吾之所以就其中。能知其是非得失之分者无他。以其知之理俱本于心中故也。智之所照。无微不烛。无物不察。则所谓妙众理。所谓宰万物者。正是智之事。抑何深斥之有哉。大抵是非之理。即智也。辨是非而是非之者。即智之知也。其所以该贮此智。运用此知者。即心也。是以就心上总言之则所谓知者。统属于心。(如爱宜别实皆属于心)就性上分言之则所谓智者。专主乎知。(如仁专主乎爱义专主乎宜礼专主乎别信专主乎实)随其所主。自不相碍。此于名义界分之际。有不可以毫釐差者。何可以其统属者。疑其专主者。而乃曰不明于心性之辨乎。仁之事非一端。义之事亦非一端。然(礼信亦然)非智则皆无以知之。故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张子曰仁不得智则不知。朱子曰智本来藏仁礼。义唯是知恁地了方恁地。然则
又曰知觉。乃智之事。若以知谓不管于智。而专为心之用则何以曰智之端。又何以曰知是非者智也。而至于所谓智之事。尤为明白的当。无少可疑也。夫智自是知底物事。凡有所知。皆主于智。故朱子以别忠佞分善恶。辨义理公私。俱谓之智。然则凡天下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有万不同。纷纭错综。不可究诘。而吾之所以就其中。能知其是非得失之分者无他。以其知之理俱本于心中故也。智之所照。无微不烛。无物不察。则所谓妙众理。所谓宰万物者。正是智之事。抑何深斥之有哉。大抵是非之理。即智也。辨是非而是非之者。即智之知也。其所以该贮此智。运用此知者。即心也。是以就心上总言之则所谓知者。统属于心。(如爱宜别实皆属于心)就性上分言之则所谓智者。专主乎知。(如仁专主乎爱义专主乎宜礼专主乎别信专主乎实)随其所主。自不相碍。此于名义界分之际。有不可以毫釐差者。何可以其统属者。疑其专主者。而乃曰不明于心性之辨乎。仁之事非一端。义之事亦非一端。然(礼信亦然)非智则皆无以知之。故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张子曰仁不得智则不知。朱子曰智本来藏仁礼。义唯是知恁地了方恁地。然则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5L 页
 仁义亦待智而后知也。夫智理也。仁义亦理也。今曰以智知仁义。则此有似于以理知理。而然从古圣贤皆如此说者。盖以智之为性。本为主知也。苟知孟子程朱之说不害于以智知理。则胡氏所谓妙众理者。又何病于以智妙理乎。朱子曰运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五性之中。信又主实。仁义礼智。非信则不实。故朱子曰信者。诚实此四者。苟如今日之疑。则信之实此四者。亦可谓以理实理。而指为之病乎。朱子曰仁统四性。是则以理统理也。张子曰仁不得义则不行。是则以理行理也。孟子曰智之实知斯二者。是则以理知理也。又曰礼者节文斯二者。是则以理节文理也。盖智之能知。犹仁之能爱义之能宜也。(礼信亦然)非仁则不能爱矣。非义则不能宜矣。然则非智则不能知者。岂不十分分晓乎。由是观之。胡氏之说。实有所据。恐不可容易打破也。惟神明二字。果似专说心之体段。然此亦不无可诿者。今以一身言之。心为一身之神明。而以一心言之。智又为一心之神明。(新安陈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此犹康节邵氏以心为太极之例也。故古人于智。指其神通处谓之神智。指其明哲处谓之明智。以此求之。所谓神明者。恐又不
仁义亦待智而后知也。夫智理也。仁义亦理也。今曰以智知仁义。则此有似于以理知理。而然从古圣贤皆如此说者。盖以智之为性。本为主知也。苟知孟子程朱之说不害于以智知理。则胡氏所谓妙众理者。又何病于以智妙理乎。朱子曰运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五性之中。信又主实。仁义礼智。非信则不实。故朱子曰信者。诚实此四者。苟如今日之疑。则信之实此四者。亦可谓以理实理。而指为之病乎。朱子曰仁统四性。是则以理统理也。张子曰仁不得义则不行。是则以理行理也。孟子曰智之实知斯二者。是则以理知理也。又曰礼者节文斯二者。是则以理节文理也。盖智之能知。犹仁之能爱义之能宜也。(礼信亦然)非仁则不能爱矣。非义则不能宜矣。然则非智则不能知者。岂不十分分晓乎。由是观之。胡氏之说。实有所据。恐不可容易打破也。惟神明二字。果似专说心之体段。然此亦不无可诿者。今以一身言之。心为一身之神明。而以一心言之。智又为一心之神明。(新安陈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此犹康节邵氏以心为太极之例也。故古人于智。指其神通处谓之神智。指其明哲处谓之明智。以此求之。所谓神明者。恐又不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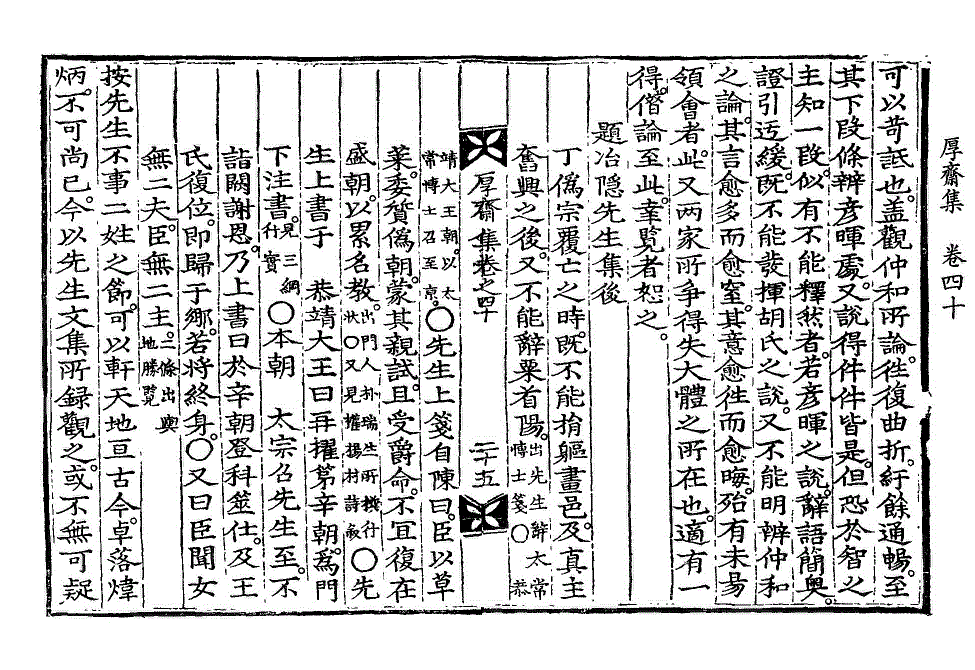 可以苛诋也。盖观仲和所论。往复曲折。纡馀通畅。至其下段条辨彦晖处。又说得件件皆是。但恐于智之主知一段。似有不能释然者。若彦晖之说。辞语简奥。證引迂缓。既不能发挥胡氏之说。又不能明辨仲和之论。其言愈多而愈窒。其意愈往而愈晦。殆有未易领会者。此又两家所争得失大体之所在也。适有一得。僭论至此。幸览者恕之。
可以苛诋也。盖观仲和所论。往复曲折。纡馀通畅。至其下段条辨彦晖处。又说得件件皆是。但恐于智之主知一段。似有不能释然者。若彦晖之说。辞语简奥。證引迂缓。既不能发挥胡氏之说。又不能明辨仲和之论。其言愈多而愈窒。其意愈往而愈晦。殆有未易领会者。此又两家所争得失大体之所在也。适有一得。僭论至此。幸览者恕之。题冶隐先生集后
丁伪宗覆亡之时。既不能捐躯画邑。及真主奋兴之后。又不能辞粟首阳。(出先生辞太常博士笺○ 恭靖大王朝。以太常博士召至京。)○先生上笺自陈曰。臣以草莱。委质伪朝。蒙其亲试。且受爵命。不宜复在盛朝。以累名教。(出门人朴瑞生所撰行状○又见权杨村诗叙)○先生上书于 恭靖大王曰再擢第辛朝。为门下注书。(见三纲行实)○本朝 太宗召先生至。不诣阙谢恩。乃上书曰于辛朝登科筮仕。及王氏复位。即归于乡。若将终身。○又曰臣闻女无二夫。臣无二主。(二条出舆地胜览)
按先生不事二姓之节。可以轩天地亘古今。卓落炜炳。不可尚已。今以先生文集所录观之。或不无可疑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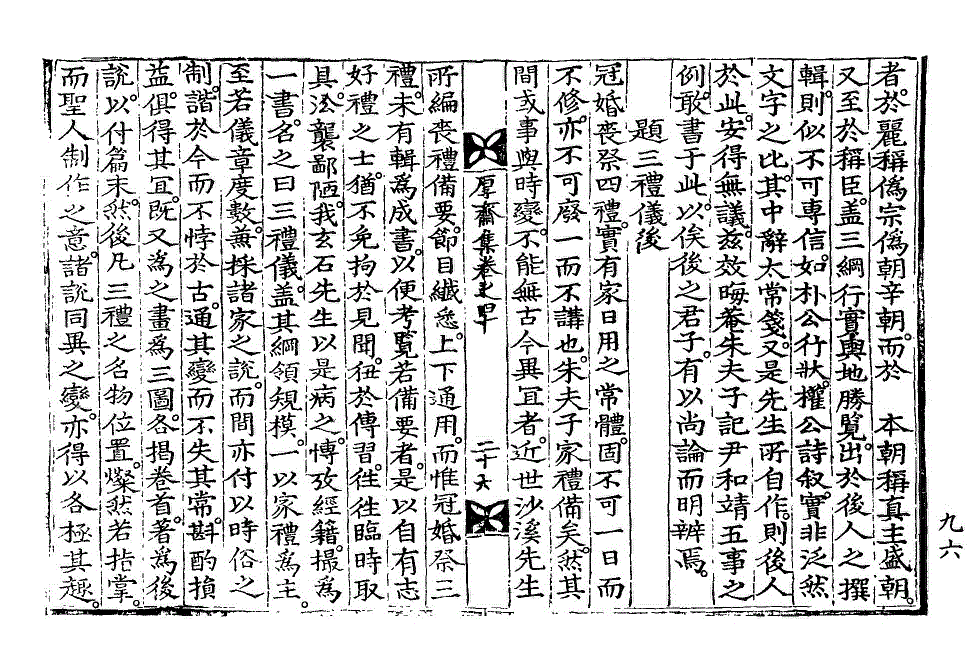 者。于丽称伪宗伪朝辛朝。而于 本朝称真主盛朝。又至于称臣。盖三纲行实,舆地胜览。出于后人之撰辑。则似不可专信。如朴公行状。权公诗叙。实非泛然文字之比。其中辞太常笺。又是先生所自作。则后人于此。安得无议。玆效晦庵朱夫子记尹和靖五事之例。敢书于此。以俟后之君子。有以尚论而明辨焉。
者。于丽称伪宗伪朝辛朝。而于 本朝称真主盛朝。又至于称臣。盖三纲行实,舆地胜览。出于后人之撰辑。则似不可专信。如朴公行状。权公诗叙。实非泛然文字之比。其中辞太常笺。又是先生所自作。则后人于此。安得无议。玆效晦庵朱夫子记尹和靖五事之例。敢书于此。以俟后之君子。有以尚论而明辨焉。题三礼仪后
冠婚丧祭四礼。实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一日而不修。亦不可废一而不讲也。朱夫子家礼备矣。然其间或事与时变。不能无古今异宜者。近世沙溪先生所编丧礼备要。节目纤悉。上下通用。而惟冠婚祭三礼。未有辑为成书。以便考览若备要者。是以自有志好礼之士。犹不免拘于见闻。狃于传习。往往临时取具。沿袭鄙陋。我玄石先生以是病之。博考经籍。撮为一书。名之曰三礼仪。盖其纲领规模。一以家礼为主。至若仪章度数。兼采诸家之说。而间亦付以时俗之制。谐于今而不悖于古。通其变而不失其常。斟酌损益。俱得其宜。既又为之画为三图。各揭卷首。著为后说。以付篇末。然后凡三礼之名物位置。灿然若指掌。而圣人制作之意。诸说同异之变。亦得以各极其趣。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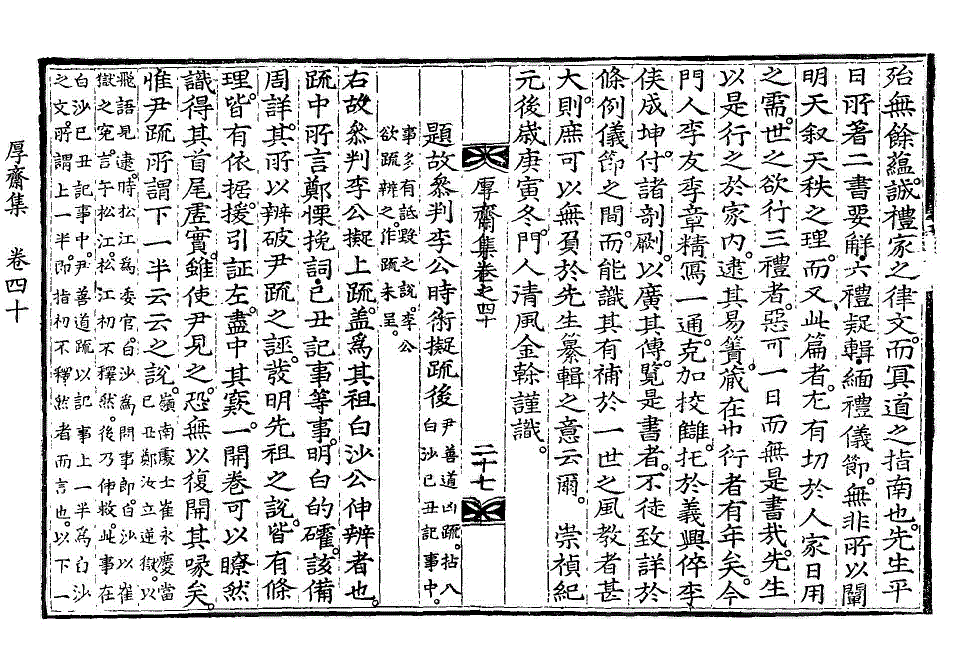 殆无馀蕴。诚礼家之律文。而冥道之指南也。先生平日所著二书要解,六礼疑辑,缅礼仪节。无非所以阐明天叙天秩之理。而又此篇者。尤有切于人家日用之需。世之欲行三礼者。恶可一日而无是书哉。先生以是行之于家内。逮其易箦。藏在巾衍者有年矣。今门人李友季章精写一通。克加校雠。托于义兴倅李侯成坤。付诸剞劂。以广其传。览是书者。不徒致详于条例仪节之间。而能识其有补于一世之风教者甚大。则庶可以无负于先生纂辑之意云尔。 崇祯纪元后岁庚寅冬。门人清风金干谨识。
殆无馀蕴。诚礼家之律文。而冥道之指南也。先生平日所著二书要解,六礼疑辑,缅礼仪节。无非所以阐明天叙天秩之理。而又此篇者。尤有切于人家日用之需。世之欲行三礼者。恶可一日而无是书哉。先生以是行之于家内。逮其易箦。藏在巾衍者有年矣。今门人李友季章精写一通。克加校雠。托于义兴倅李侯成坤。付诸剞劂。以广其传。览是书者。不徒致详于条例仪节之间。而能识其有补于一世之风教者甚大。则庶可以无负于先生纂辑之意云尔。 崇祯纪元后岁庚寅冬。门人清风金干谨识。题故参判李公时术拟疏后(尹善道凶疏。拈入白沙己丑记事中。事多有诋毁之说。李公欲疏辨之。作疏未呈。)
右故参判李公拟上疏。盖为其祖白沙公伸辨者也。疏中所言郑慄挽词,己丑记事等事。明白的礭。该备周详。其所以辨破尹疏之诬。发明先祖之说。皆有条理。皆有依据。援引证左。尽中其窾。一开卷可以瞭然识得其首尾虚实。虽使尹见之。恐无以复开其喙矣。惟尹疏所谓下一半云云之说。(岭南处士崔永庆当己丑郑汝立逆狱。以飞语见逮。时松江为委官。白沙为问事郎。白沙以崔狱之冤。言于松江。松江初不释然。后乃伸救。此事在白沙己丑记事中。尹善道疏以记事上一半为白沙之文。所谓上一半。即指初不释然者而言也。以下一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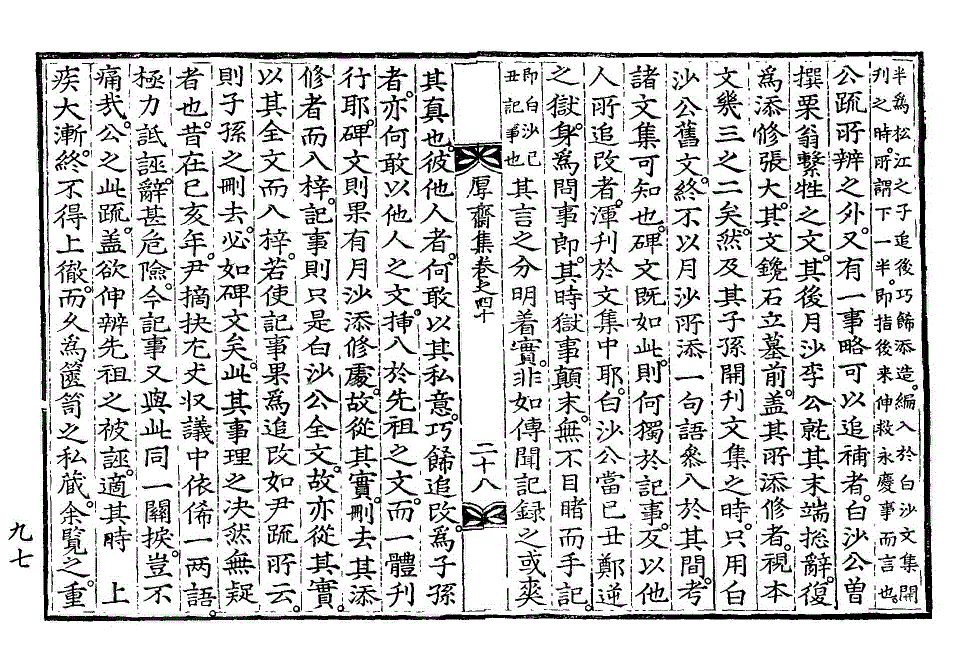 半为松江之子追后巧饰添造。编入于白沙文集开刊之时。所谓下一半。即指后来伸救永庆事而言也。)公疏所辨之外。又有一事略可以追补者。白沙公曾撰栗翁系牲之文。其后月沙李公就其末端总辞。复为添修张大。其文镵石立墓前。盖其所添修者。视本文几三之二矣。然及其子孙开刊文集之时。只用白沙公旧文。终不以月沙所添一句语参入于其间。考诸文集可知也。碑文既如此。则何独于记事。反以他人所追改者。浑刊于文集中耶。白沙公当己丑郑逆之狱。身为问事郎。其时狱事颠末。无不目睹而手记。(即白沙己丑记事也)其言之分明着实。非如传闻记录之或爽其真也。彼他人者。何敢以其私意。巧饰追改。为子孙者。亦何敢以他人之文。插入于先祖之文。而一体刊行耶。碑文则果有月沙添修处。故从其实。删去其添修者而入梓。记事则只是白沙公全文。故亦从其实。以其全文而入梓。若使记事果为追改如尹疏所云。则子孙之删去。必如碑文矣。此其事理之决然无疑者也。昔在己亥年。尹摘抉尤丈收议中依俙一两语。极力诋诬。辞甚危险。今记事又与此同一关捩。岂不痛哉。公之此疏。盖欲伸辨先祖之被诬。适其时 上疾大渐。终不得上彻。而久为箧笥之私藏。余览之。重
半为松江之子追后巧饰添造。编入于白沙文集开刊之时。所谓下一半。即指后来伸救永庆事而言也。)公疏所辨之外。又有一事略可以追补者。白沙公曾撰栗翁系牲之文。其后月沙李公就其末端总辞。复为添修张大。其文镵石立墓前。盖其所添修者。视本文几三之二矣。然及其子孙开刊文集之时。只用白沙公旧文。终不以月沙所添一句语参入于其间。考诸文集可知也。碑文既如此。则何独于记事。反以他人所追改者。浑刊于文集中耶。白沙公当己丑郑逆之狱。身为问事郎。其时狱事颠末。无不目睹而手记。(即白沙己丑记事也)其言之分明着实。非如传闻记录之或爽其真也。彼他人者。何敢以其私意。巧饰追改。为子孙者。亦何敢以他人之文。插入于先祖之文。而一体刊行耶。碑文则果有月沙添修处。故从其实。删去其添修者而入梓。记事则只是白沙公全文。故亦从其实。以其全文而入梓。若使记事果为追改如尹疏所云。则子孙之删去。必如碑文矣。此其事理之决然无疑者也。昔在己亥年。尹摘抉尤丈收议中依俙一两语。极力诋诬。辞甚危险。今记事又与此同一关捩。岂不痛哉。公之此疏。盖欲伸辨先祖之被诬。适其时 上疾大渐。终不得上彻。而久为箧笥之私藏。余览之。重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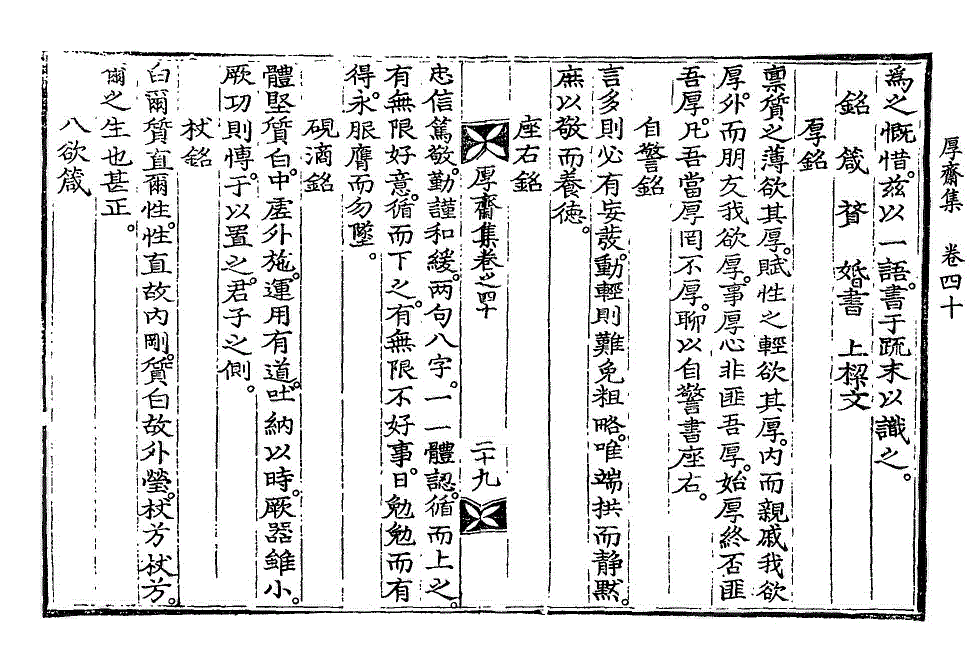 为之慨惜。玆以一语。书于疏末以识之。
为之慨惜。玆以一语。书于疏末以识之。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铭
厚铭
禀质之薄欲其厚。赋性之轻欲其厚。内而亲戚我欲厚。外而朋友我欲厚。事厚心非匪吾厚。始厚终否匪吾厚。凡吾当厚罔不厚。聊以自警书座右。
自警铭
言多则必有妄发。动轻则难免粗略。唯端拱而静默。庶以敬而养德。
座右铭
忠信笃敬。勤谨和缓。两句八字。一一体认。循而上之。有无限好意。循而下之。有无限不好事。日勉勉而有得。永服膺而勿坠。
砚滴铭
体坚质白。中虚外施。运用有道。吐纳以时。厥器虽小。厥功则博。于以置之。君子之侧。
杖铭
白尔质直尔性。性直故内刚。质白故外莹。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箴
八欲箴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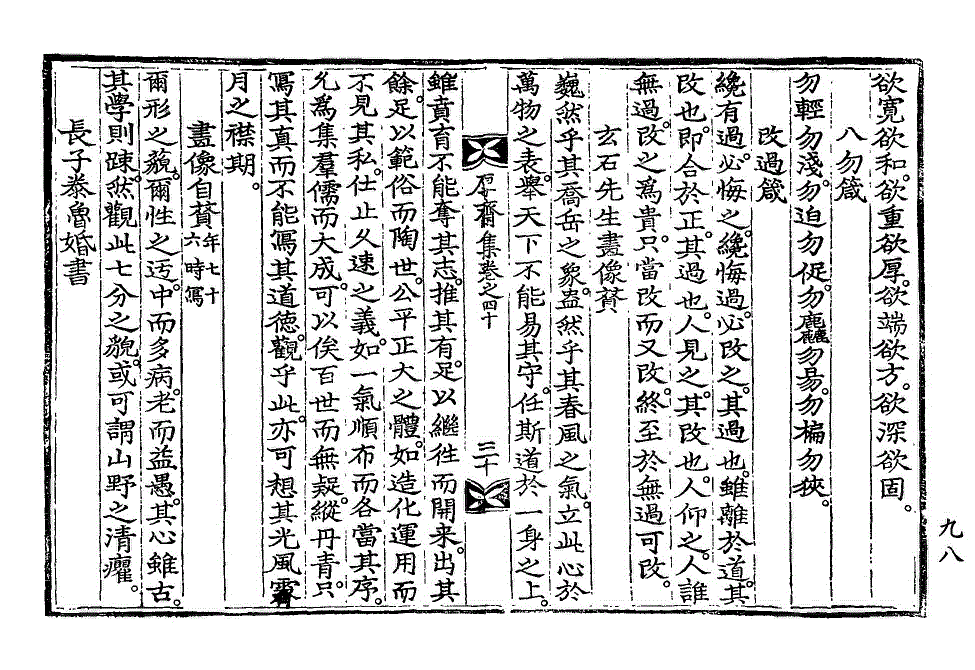 欲宽欲和。欲重欲厚。欲端欲方。欲深欲固。
欲宽欲和。欲重欲厚。欲端欲方。欲深欲固。八勿箴
勿轻勿浅。勿迫勿促。勿粗勿易。勿楄勿狭。
改过箴
才有过。必悔之。才悔过。必改之。其过也。虽离于道。其改也。即合于正。其过也。人见之。其改也。人仰之。人谁无过。改之为贵。只当改而又改。终至于无过可改。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赞
玄石先生画像赞
巍然乎其乔岳之象。盎然乎其春风之气。立此心于万物之表。举天下不能易其守。任斯道于一身之上。虽贲育不能夺其志。推其有。足以继往而开来。出其馀。足以范俗而陶世。公平正大之体。如造化运用而不见其私。仕止久速之义。如一气顺布而各当其序。允为集群儒而大成。可以俟百世而无疑。纵丹青。只写其真而不能写其道德。观乎此。亦可想其光风霁月之襟期。
画像自赞(年七十六时写)
尔形之藐。尔性之迂。中而多病。老而益愚。其心虽古。其学则疏。然观此七分之貌。或可谓山野之清癯。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婚书
长子泰鲁婚书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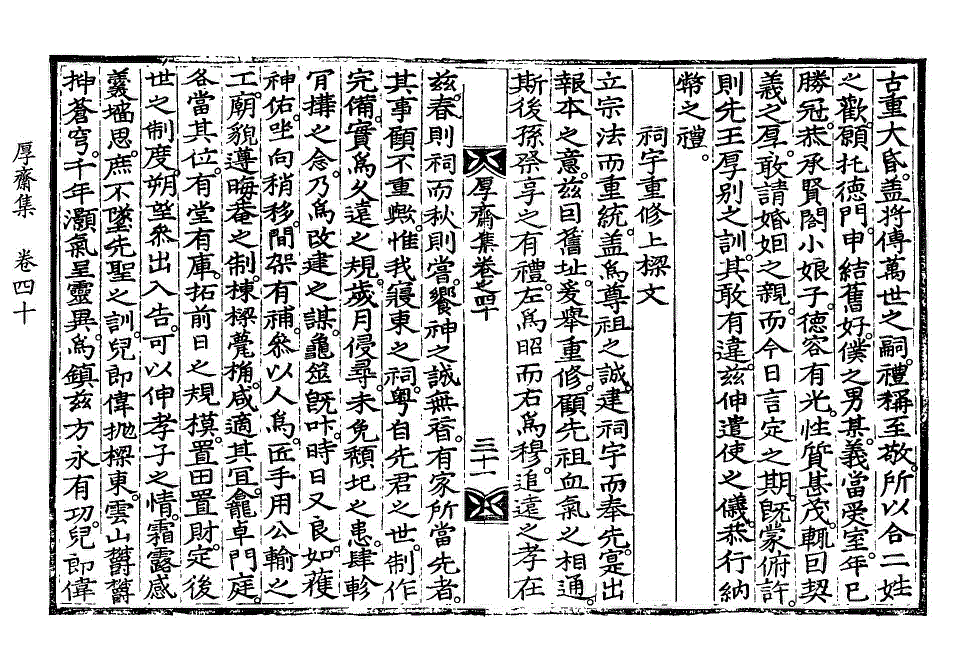 古重大昏。盖将传万世之嗣。礼称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欢。愿托德门。申结旧好。仆之男某。义当受室。年已胜冠。恭承贤閤小娘子。德容有光。性质甚茂。辄因契义之厚。敢请婚姻之亲。而今日言定之期。既蒙俯许。则先王厚别之训。其敢有违。玆伸遣使之仪。恭行纳币之礼。
古重大昏。盖将传万世之嗣。礼称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欢。愿托德门。申结旧好。仆之男某。义当受室。年已胜冠。恭承贤閤小娘子。德容有光。性质甚茂。辄因契义之厚。敢请婚姻之亲。而今日言定之期。既蒙俯许。则先王厚别之训。其敢有违。玆伸遣使之仪。恭行纳币之礼。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上梁文
祠宇重修上梁文
立宗法而重统。盖为尊祖之诚。建祠宇而奉先。寔出报本之意。玆因旧址。爰举重修。顾先祖血气之相通。斯后孙祭享之有礼。左为昭而右为穆。追远之孝在玆。春则祠而秋则尝。飨神之诚无替。有家所当先者。其事顾不重欤。惟我寝东之祠。粤自先君之世。制作完备。实为久远之规。岁月侵寻。未免颓圮之患。肆轸肯搆之念。乃为改建之谋。龟筮既叶。时日又良。如获神佑。坐向稍移。间架有补。参以人为。匠手用公输之工。庙貌遵晦庵之制。栋梁甍桷。咸适其宜。龛卓门庭。各当其位。有堂有库。拓前日之规模。置田置财。定后世之制度。朔望参出入告。可以伸孝子之情。霜露感羹墙思。庶不坠先圣之训。儿郎伟抛梁东。云山郁郁抻苍穹。千年灏气呈灵异。为镇玆方永有功。儿郎伟
厚斋先生集卷之四十 第 99L 页
 抛梁西。五峰崒嵂与天齐。长令风气无疏泄。修岳冠山视却低。儿郎伟抛梁南。苍崖朝暮起烟岚。淙淙更有惺心处。一派鸣泉泻石潭。儿郎伟抛梁北。园有茱萸兼枣栗。岁暮田家生理饶。享仪从此膺休福。儿郎伟抛梁上。日月高悬不可仰。无数烟霞藏此中。四时光景助清赏。儿郎伟抛梁下。循除溪水流其左。千秋福地在玆间。日出人烟满四野。伏愿上梁之后。灾沴尽绝。福祥毕兴。阳俎阴笾。常荐芬苾之享。前堂后寝。永作子孙之传。
抛梁西。五峰崒嵂与天齐。长令风气无疏泄。修岳冠山视却低。儿郎伟抛梁南。苍崖朝暮起烟岚。淙淙更有惺心处。一派鸣泉泻石潭。儿郎伟抛梁北。园有茱萸兼枣栗。岁暮田家生理饶。享仪从此膺休福。儿郎伟抛梁上。日月高悬不可仰。无数烟霞藏此中。四时光景助清赏。儿郎伟抛梁下。循除溪水流其左。千秋福地在玆间。日出人烟满四野。伏愿上梁之后。灾沴尽绝。福祥毕兴。阳俎阴笾。常荐芬苾之享。前堂后寝。永作子孙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