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x 页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书
书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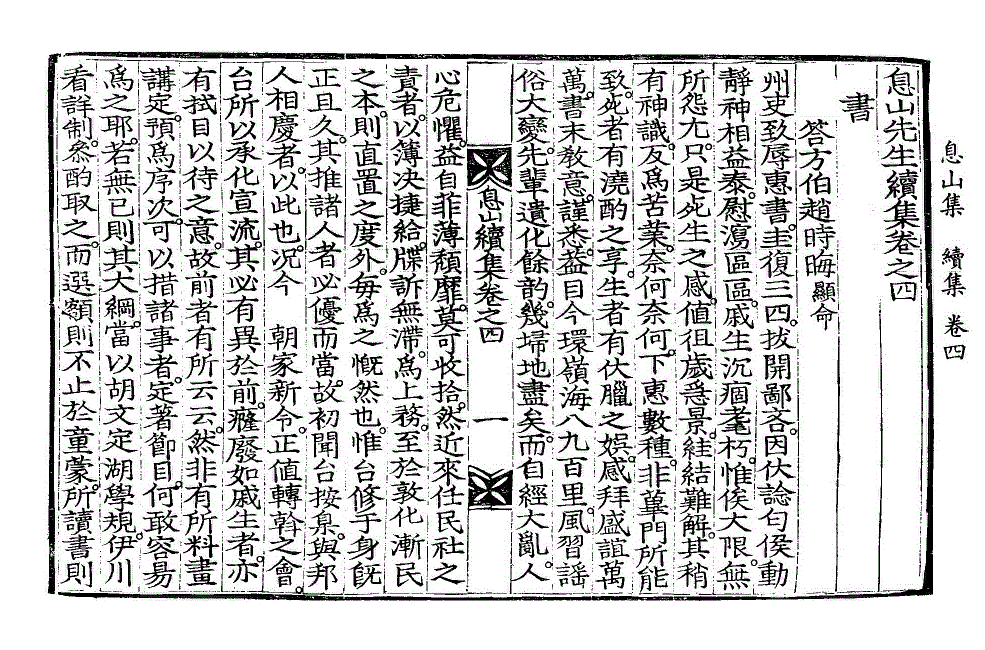 答方伯赵时晦(显命)
答方伯赵时晦(显命)州吏致辱惠书。圭复三四。拔开鄙吝。因伏谂匀侯动静神相益泰。慰泻区区。戚生沉痼耄朽。惟俟大限。无所怨尤。只是死生之感。值徂岁急景。絓结难解。其稍有神识。反为苦业。奈何奈何。下惠数种。非荜门所能致。死者有浇酌之享。生者有伏腊之娱。感拜盛谊万万。书末教意。谨悉。盖目今环岭海八九百里。风习谣俗大变。先辈遗化馀韵。几埽地尽矣。而自经大乱。人心危惧。益自菲薄颓靡。莫可收拾。然近来任民社之责者。以簿决捷给。牒诉无滞。为上务。至于敦化渐民之本。则直置之度外。每为之慨然也。惟台修于身既正且久。其推诸人者必优而当。故初闻台按臬。与邦人相庆者。以此也。况今 朝家新令。正值转斡之会。台所以承化宣流。其必有异于前。癃废如戚生者。亦有拭目以待之意。故前者有所云云。然非有所料画讲定。预为序次。可以措诸事者。定著节目。何敢容易为之耶。若无已则其大纲。当以胡文定湖学规。伊川看详制。参酌取之。而选额则不止于童蒙。所读书则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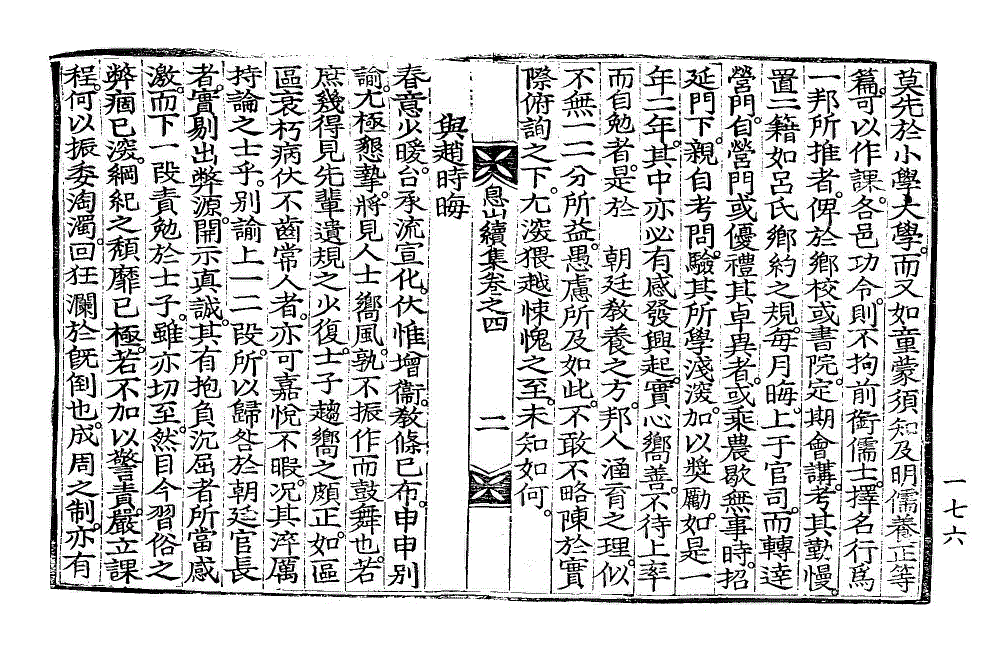 莫先于小学,大学。而又如童蒙须知及明儒养正等篇。可以作课。各邑功令。则不拘前衔儒士。择名行为一邦所推者。俾于乡校或书院。定期会讲。考其勤慢。置二籍如吕氏乡约之规。每月晦。上于官司。而转达营门。自营门或优礼其卓异者。或乘农歇无事时。招延门下。亲自考问。验其所学浅深。加以奖励。如是一年二年。其中亦必有感发兴起。实心向善。不待上率而自勉者。是于 朝廷教养之方。邦人涵育之理。似不无一二分所益。愚虑所及如此。不敢不略陈于实际俯询之下。尤深猥越悚愧之至。未知如何。
莫先于小学,大学。而又如童蒙须知及明儒养正等篇。可以作课。各邑功令。则不拘前衔儒士。择名行为一邦所推者。俾于乡校或书院。定期会讲。考其勤慢。置二籍如吕氏乡约之规。每月晦。上于官司。而转达营门。自营门或优礼其卓异者。或乘农歇无事时。招延门下。亲自考问。验其所学浅深。加以奖励。如是一年二年。其中亦必有感发兴起。实心向善。不待上率而自勉者。是于 朝廷教养之方。邦人涵育之理。似不无一二分所益。愚虑所及如此。不敢不略陈于实际俯询之下。尤深猥越悚愧之至。未知如何。与赵时晦
春意少暖。台承流宣化。伏惟增卫。教条已布。申申别谕。尤极恳挚。将见人士向风。孰不振作而鼓舞也。若庶几得见先辈遗规之少复。士子趋向之颇正。如区区衰朽病伏不齿常人者。亦可嘉悦不暇。况其淬厉持论之士乎。别谕上一二段。所以归咎于朝廷官长者。实剔出弊源。开示真诚。其有抱负沉屈者所当感激。而下一段责勉于士子。虽亦切至。然目今习俗之弊痼已深。纲纪之颓靡已极。若不加以警责。严立课程。何以振委淘浊。回狂澜于既倒也。成周之制。亦有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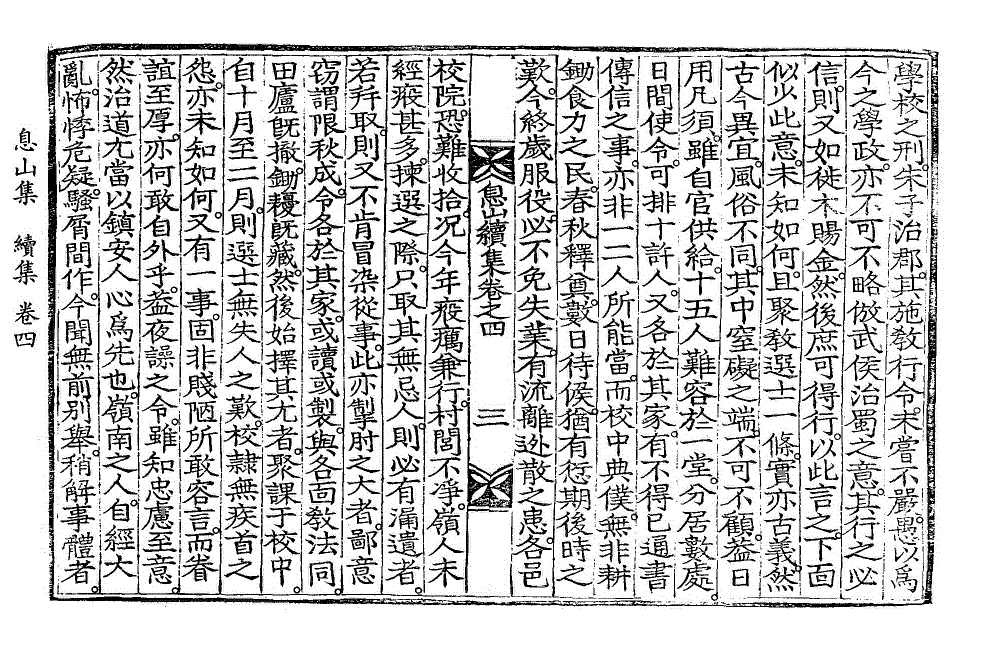 学校之刑。朱子治郡。其施教行令。未尝不严。愚以为今之学政。亦不可不略仿武侯治蜀之意。其行之必信。则又如徙木赐金。然后庶可得行。以此言之。下面似少此意。未知如何。且聚教选士一条。实亦古义。然古今异宜。风俗不同。其中窒碍之端。不可不顾。盖日用凡须。虽自官供给。十五人难容于一堂。分居数处。日间使令。可排十许人。又各于其家。有不得已通书传信之事。亦非一二人所能当。而校中典仆。无非耕锄食力之民。春秋释奠。数日待候。犹有愆期后时之叹。今终岁服役。必不免失业。有流离逃散之患。各邑校院。恐难收拾。况今年疫疠兼行。村闾不净。岭人未经疫甚多。拣选之际。只取其无忌人。则必有漏遗者。若并取。则又不肯冒染从事。此亦掣肘之大者。鄙意窃谓限秋成。令各于其家。或读或制。与各面教法同。田庐既撤。锄耰既藏。然后始择其尤者。聚课于校中。自十月至二月。则选士无失人之叹。校隶无疾首之怨。亦未知如何。又有一事。固非贱陋所敢容言。而眷谊至厚。亦何敢自外乎。盖夜噪之令。虽知忠虑至意。然治道尤当以镇安人心为先也。岭南之人。自经大乱。怖悸危疑。骚屑间作。今闻无前别举。稍解事体者。
学校之刑。朱子治郡。其施教行令。未尝不严。愚以为今之学政。亦不可不略仿武侯治蜀之意。其行之必信。则又如徙木赐金。然后庶可得行。以此言之。下面似少此意。未知如何。且聚教选士一条。实亦古义。然古今异宜。风俗不同。其中窒碍之端。不可不顾。盖日用凡须。虽自官供给。十五人难容于一堂。分居数处。日间使令。可排十许人。又各于其家。有不得已通书传信之事。亦非一二人所能当。而校中典仆。无非耕锄食力之民。春秋释奠。数日待候。犹有愆期后时之叹。今终岁服役。必不免失业。有流离逃散之患。各邑校院。恐难收拾。况今年疫疠兼行。村闾不净。岭人未经疫甚多。拣选之际。只取其无忌人。则必有漏遗者。若并取。则又不肯冒染从事。此亦掣肘之大者。鄙意窃谓限秋成。令各于其家。或读或制。与各面教法同。田庐既撤。锄耰既藏。然后始择其尤者。聚课于校中。自十月至二月。则选士无失人之叹。校隶无疾首之怨。亦未知如何。又有一事。固非贱陋所敢容言。而眷谊至厚。亦何敢自外乎。盖夜噪之令。虽知忠虑至意。然治道尤当以镇安人心为先也。岭南之人。自经大乱。怖悸危疑。骚屑间作。今闻无前别举。稍解事体者。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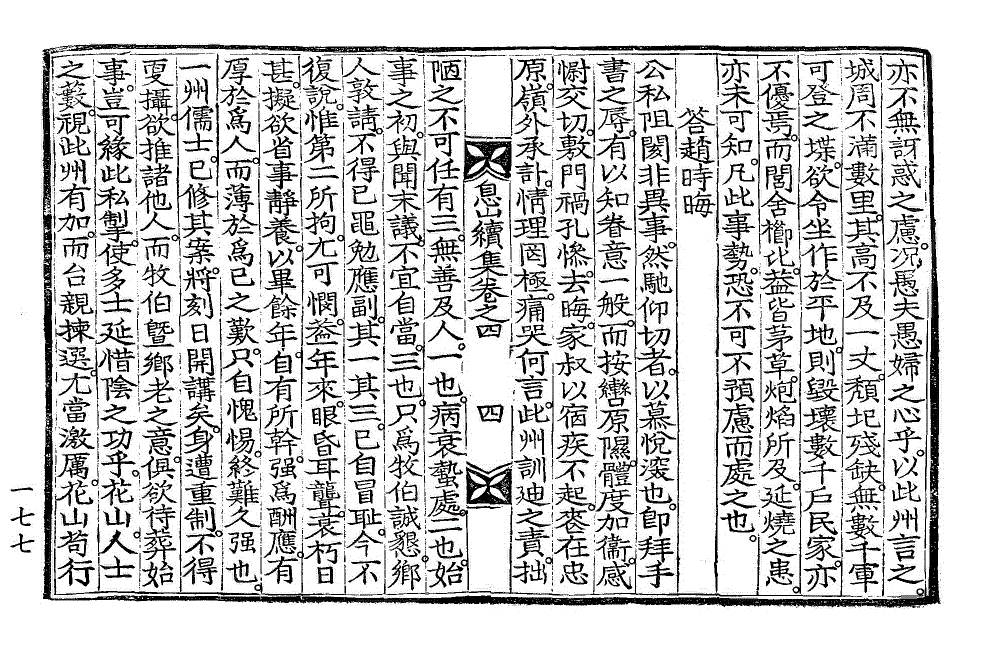 亦不无讶惑之虑。况愚夫愚妇之心乎。以此州言之。城周不满数里。其高不及一丈。颓圮残缺。无数千军可登之堞。欲令坐作于平地。则毁坏数千户民家。亦不优焉。而闾舍栉比。盖皆茅草。炮焰所及。延烧之患。亦未可知。凡此事势。恐不可不预虑而处之也。
亦不无讶惑之虑。况愚夫愚妇之心乎。以此州言之。城周不满数里。其高不及一丈。颓圮残缺。无数千军可登之堞。欲令坐作于平地。则毁坏数千户民家。亦不优焉。而闾舍栉比。盖皆茅草。炮焰所及。延烧之患。亦未可知。凡此事势。恐不可不预虑而处之也。答赵时晦
公私阻阂非异事。然驰仰切者。以慕悦深也。即拜手书之辱。有以知眷意一般。而按辔原隰。体度加卫。感慰交切。敷门祸孔惨。去晦。家叔以宿疾不起。丧在忠原。岭外承讣。情理罔极。痛哭何言。此州训迪之责。拙陋之不可任有三。无善及人。一也。病衰蛰处。二也。始事之初。与闻末议。不宜自当。三也。只为牧伯诚恳。乡人敦请。不得已黾勉应副。其一其三。已自冒耻。今不复说。惟第二所拘。尤可悯。盖年来。眼昏耳聋。衰朽日甚。拟欲省事静养。以毕馀年。自有所干。强为酬应。有厚于为人。而薄于为己之叹。只自愧惕。终难久强也。一州儒士。已修其案。将刻日开讲矣。身遭重制。不得更摄。欲推诸他人。而牧伯暨乡老之意。俱欲待葬始事。岂可缘此私掣。使多士延惜阴之功乎。花山。人士之薮。视此州有加。而台亲拣选。尤当激厉。花山苟行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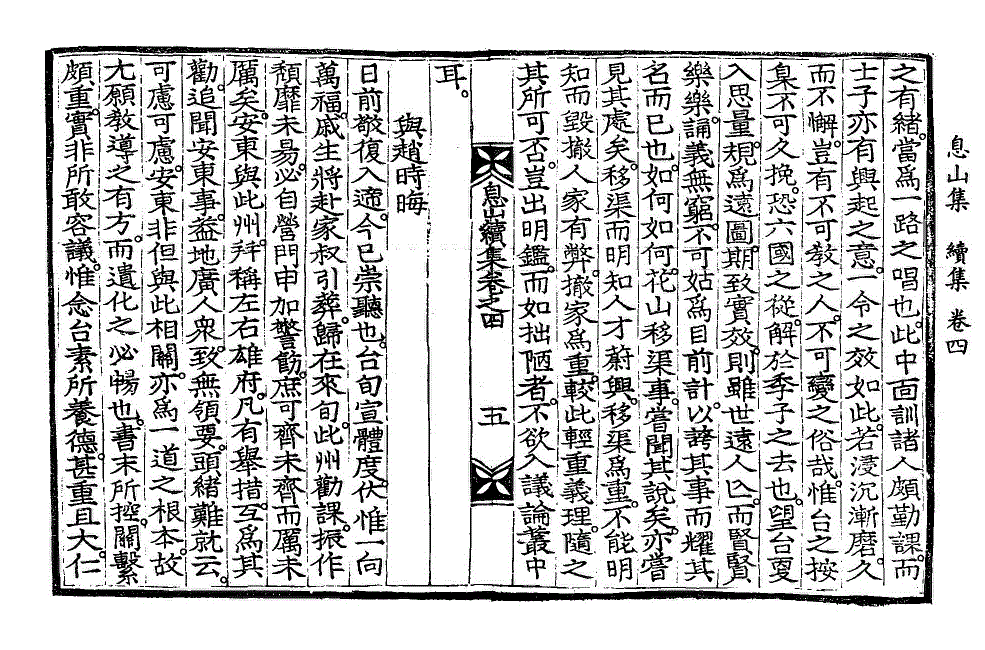 之有绪。当为一路之唱也。此中面训诸人颇勤课。而士子亦有兴起之意。一令之效如此。若浸沉渐磨。久而不懈。岂有不可教之人。不可变之俗哉。惟台之按臬不可久挽。恐六国之从。解于季子之去也。望台更入思量。规为远图。期致实效。则虽世远人亡。而贤贤乐乐。诵义无穷。不可姑为目前计。以誇其事而耀其名而已也。如何如何。花山移渠事。尝闻其说矣。亦尝见其处矣。移渠而明知人才蔚兴。移渠为重。不能明知而毁撤人家有弊。撤家为重。较此轻重义理。随之其所可否。岂出明鉴。而如拙陋者。不欲入议论丛中耳。
之有绪。当为一路之唱也。此中面训诸人颇勤课。而士子亦有兴起之意。一令之效如此。若浸沉渐磨。久而不懈。岂有不可教之人。不可变之俗哉。惟台之按臬不可久挽。恐六国之从。解于季子之去也。望台更入思量。规为远图。期致实效。则虽世远人亡。而贤贤乐乐。诵义无穷。不可姑为目前计。以誇其事而耀其名而已也。如何如何。花山移渠事。尝闻其说矣。亦尝见其处矣。移渠而明知人才蔚兴。移渠为重。不能明知而毁撤人家有弊。撤家为重。较此轻重义理。随之其所可否。岂出明鉴。而如拙陋者。不欲入议论丛中耳。与赵时晦
日前敬复入遆。今已崇听也。台旬宣体度。伏惟一向万福。戚生将赴家叔引葬。归在来旬。此州劝课。振作颓靡未易。必自营门申加警饬。庶可齐未齐而厉未厉矣。安东与此州。并称左右雄府。凡有举措。互为其劝。追闻安东事。盖地广人众。致无领要。头绪难就云。可虑可虑。安东非但与此相关。亦为一道之根本。故尤愿教导之有方。而遗化之必畅也。书末所控。关系颇重。实非所敢容议。惟念台素所养德。甚重且大。仁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8L 页
 声仁闻。洽于一方。如或少失于中。其平日慕悦往复者。与有责焉。可不勉乎。官裨军法之令。虽出于严肃纪律之意。然愚窃以为过矣。盖其所犯。只在循习谬例而已。与军中聚敛差间。则以宁失不经之义处之。似或可乎。言出肝肺。亦无以督过焉。
声仁闻。洽于一方。如或少失于中。其平日慕悦往复者。与有责焉。可不勉乎。官裨军法之令。虽出于严肃纪律之意。然愚窃以为过矣。盖其所犯。只在循习谬例而已。与军中聚敛差间。则以宁失不经之义处之。似或可乎。言出肝肺。亦无以督过焉。答赵时晦
旱炎益肆。台候动静如何。伏惟加卫。戚生忠原往返。撼顿致疾。益无人状。非徒情理之痛绝也。乾旱此酷。金豕降灾。岂是六运之必臻耶。漆室之忧。不但在一身之口腹。况台任千里分忧之重。将何以料度经纪。救百万喁喁之命也。两麦始及输场。而太半枯壳。注秧亦已过限。而沟洫龟坼。牧伯追日斋洁。躬行祷祝。里妪田叟。亦感其诚。而终无霢霂浥尘。天意漠漠。为之奈何。境内埋沉副辜凡数处。祈事毕。则牧伯欲驰进奉议云。盖以安东之幅员。晋州之田结。而民户之多。俱不及尚。台所以指画区处。宜不可与他州县等。如何如何。劝课一事。近颇有绪。诸院诸塾。所在坌集。不似向来枵然一室徒拥虚名者。此亦官长奉行勤干所致。但未尝不以近里工夫相勉。而前有利诱之期。辄浸浸向词章偏了。更愿用大炉鞴锻鍊而出也。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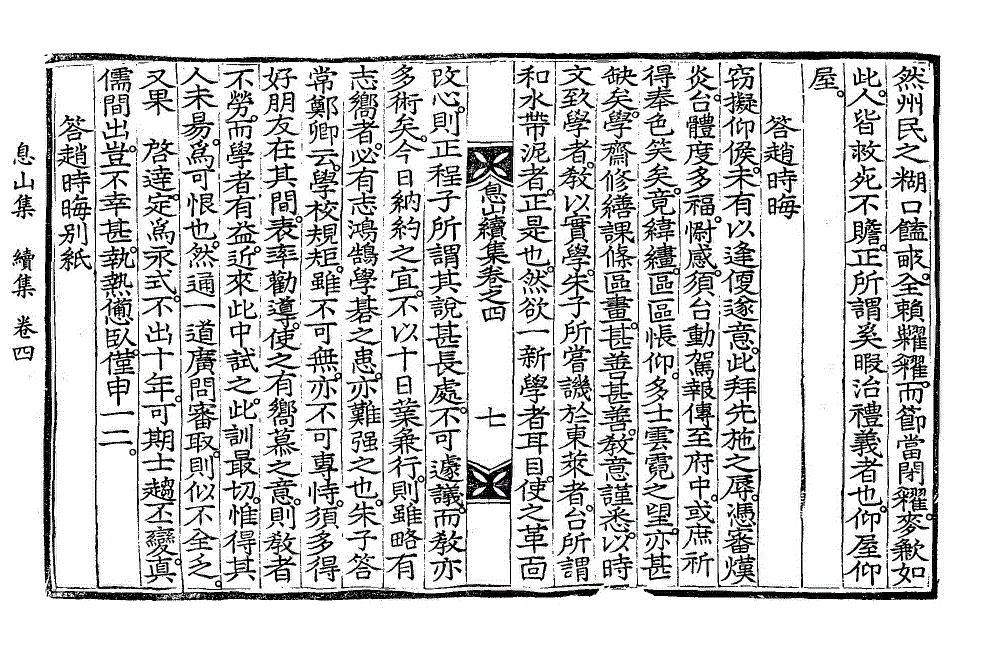 然州民之糊口馌亩。全赖粜籴。而节当闭籴。麦歉如此。人皆救死不赡。正所谓奚暇治礼义者也。仰屋仰屋。
然州民之糊口馌亩。全赖粜籴。而节当闭籴。麦歉如此。人皆救死不赡。正所谓奚暇治礼义者也。仰屋仰屋。答赵时晦
窃拟仰候。未有以逢便遂意。此拜先施之辱。凭审熯炎。台体度多福。慰感。须台动驾报传至府中。或庶祈得奉色笑矣。竟纬繣。区区怅仰。多士云霓之望。亦甚缺矣。学斋修缮课条区画。甚善甚善。教意谨悉。以时文致学者。教以实学。朱子所尝讥于东莱者。台所谓和水带泥者。正是也。然欲一新学者耳目。使之革面改心。则正程子所谓其说甚长处。不可遽议。而教亦多术矣。今日纳约之宜。不以十日业兼行。则虽略有志向者。必有志鸿鹄学棋之患。亦难强之也。朱子答常郑卿云。学校规
答赵时晦别纸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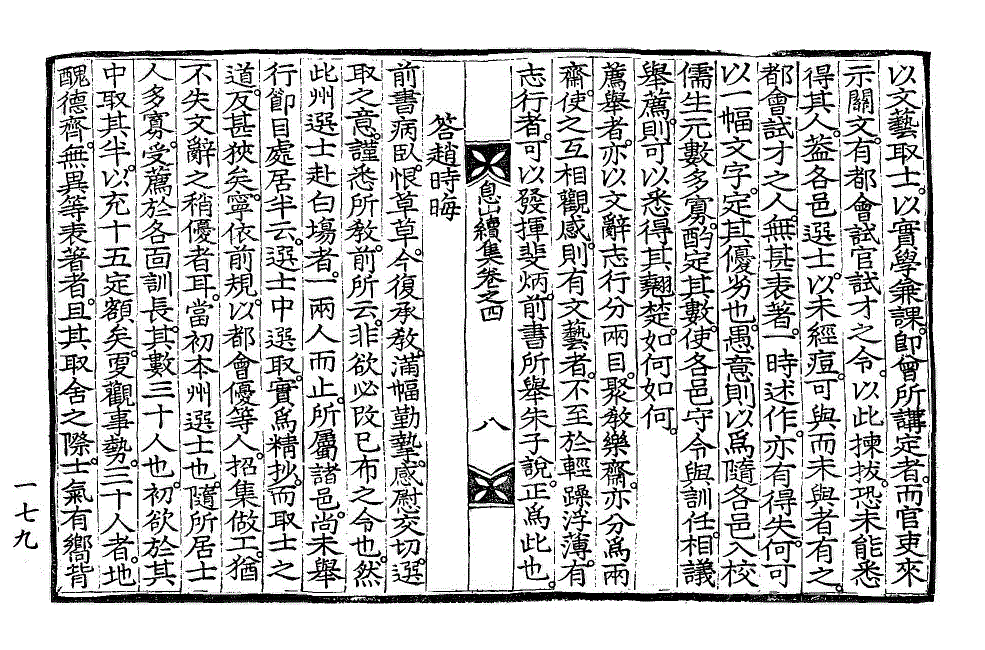 以文艺取士。以实学兼课。即曾所讲定者。而官吏来示关文。有都会试官试才之令。以此拣拔。恐未能悉得其人。盖各邑选士。以未经痘。可与而未与者有之。都会试才之人。无甚表著。一时述作。亦有得失。何可以一幅文字。定其优劣也。愚意则以为随各邑入校儒生元数多寡。酌定其数。使各邑守令与训任。相议举荐。则可以悉得其翘楚。如何如何。
以文艺取士。以实学兼课。即曾所讲定者。而官吏来示关文。有都会试官试才之令。以此拣拔。恐未能悉得其人。盖各邑选士。以未经痘。可与而未与者有之。都会试才之人。无甚表著。一时述作。亦有得失。何可以一幅文字。定其优劣也。愚意则以为随各邑入校儒生元数多寡。酌定其数。使各邑守令与训任。相议举荐。则可以悉得其翘楚。如何如何。荐举者。亦以文辞志行分两目。聚教乐斋。亦分为两斋。使之互相观感。则有文艺者。不至于轻躁浮薄。有志行者。可以发挥斐炳。前书所举朱子说。正为此也。
答赵时晦
前书病卧。恨草草。今复承教。满幅勤挚。感慰交切。选取之意。谨悉所教。前所云。非欲必改已布之令也。然此州选士赴白场者。一两人而止。所属诸邑。尚未举行节目处居半云。选士中选取。实为精抄。而取士之道。反甚狭矣。宁依前规。以都会优等人。招集做工。犹不失文辞之稍优者耳。当初本州选士也。随所居士人多寡。受荐于各面训长。其数三十人也。初欲于其中取其半。以充十五定额矣。更观事势。三十人者。地丑德齐。无异等表著者。且其取舍之际。士气有向背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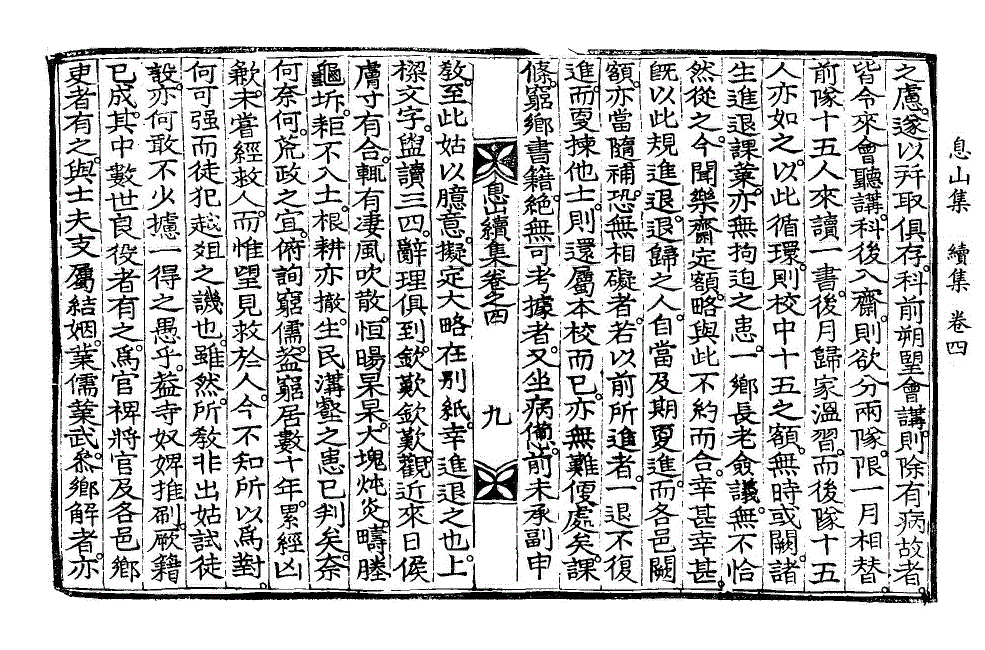 之虑。遂以并取俱存。科前朔望会讲。则除有病故者。皆令来会听讲。科后入斋。则欲分两队。限一月相替。前队十五人来读一书。后月归家温习。而后队十五人亦如之。以此循环。则校中十五之额。无时或阙。诸生进退课业。亦无拘迫之患。一乡长老佥议。无不恰然从之。今闻乐斋定额。略与此不约而合。幸甚幸甚。既以此规进退。退归之人。自当及期更进。而各邑阙额。亦当随补。恐无相碍者。若以前所进者。一退不复进。而更拣他士。则还属本校而已。亦无难便处矣。课条。穷乡书籍。绝无可考据者。又坐病惫。前未承副申教。至此姑以臆意。拟定大略在别纸。幸进退之也。上梁文字。盥读三四。辞理俱到。钦叹钦叹。观近来日候肤寸有合。辄有凄风吹散。恒旸杲杲。大块炖炎。畴塍龟坼。耟不入土。根耕亦撤。生民沟壑之患已判矣。奈何奈何。荒政之宜。俯询穷儒。盖穷居数十年。累经凶歉。未尝经救人。而惟望见救于人。今不知所以为对。何可强而徒犯越俎之讥也。虽然。所教非出姑试徒设。亦何敢不少摅一得之愚乎。盖寺奴婢推刷。厥籍已成。其中数世良役者有之。为官裨将官及各邑乡吏者有之。与士夫支属结姻。业儒业武。参乡解者。亦
之虑。遂以并取俱存。科前朔望会讲。则除有病故者。皆令来会听讲。科后入斋。则欲分两队。限一月相替。前队十五人来读一书。后月归家温习。而后队十五人亦如之。以此循环。则校中十五之额。无时或阙。诸生进退课业。亦无拘迫之患。一乡长老佥议。无不恰然从之。今闻乐斋定额。略与此不约而合。幸甚幸甚。既以此规进退。退归之人。自当及期更进。而各邑阙额。亦当随补。恐无相碍者。若以前所进者。一退不复进。而更拣他士。则还属本校而已。亦无难便处矣。课条。穷乡书籍。绝无可考据者。又坐病惫。前未承副申教。至此姑以臆意。拟定大略在别纸。幸进退之也。上梁文字。盥读三四。辞理俱到。钦叹钦叹。观近来日候肤寸有合。辄有凄风吹散。恒旸杲杲。大块炖炎。畴塍龟坼。耟不入土。根耕亦撤。生民沟壑之患已判矣。奈何奈何。荒政之宜。俯询穷儒。盖穷居数十年。累经凶歉。未尝经救人。而惟望见救于人。今不知所以为对。何可强而徒犯越俎之讥也。虽然。所教非出姑试徒设。亦何敢不少摅一得之愚乎。盖寺奴婢推刷。厥籍已成。其中数世良役者有之。为官裨将官及各邑乡吏者有之。与士夫支属结姻。业儒业武。参乡解者。亦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0L 页
 有之。名分之紊。固可惋。而因循已久。一朝还贱。俱有抑郁之意也。想此类在在有之。而亦当有产业优足者。使之入粟许赎。随其口之多寡。定粟之数。则七十州所得之粟。可通计数十万石。足以救颠连滨死之命。岂不幸甚。然此事必 启达蒙 允。可以行之。如不以为不可。须预料区处。可无后时之叹也。如以 朝家新令才成。遽请募赎为难。是亦不然。朱子尝请给度牒。推偿献助人。十分勤恳。又与宰相书。申申不已。此比度牒推偿。似无轻重。我 圣上圣德至仁。恻怛普博。亦必快从无难矣。如何如何。
有之。名分之紊。固可惋。而因循已久。一朝还贱。俱有抑郁之意也。想此类在在有之。而亦当有产业优足者。使之入粟许赎。随其口之多寡。定粟之数。则七十州所得之粟。可通计数十万石。足以救颠连滨死之命。岂不幸甚。然此事必 启达蒙 允。可以行之。如不以为不可。须预料区处。可无后时之叹也。如以 朝家新令才成。遽请募赎为难。是亦不然。朱子尝请给度牒。推偿献助人。十分勤恳。又与宰相书。申申不已。此比度牒推偿。似无轻重。我 圣上圣德至仁。恻怛普博。亦必快从无难矣。如何如何。别纸乐育斋节目。
本斋。乃前辈所创。其意虽美。然只聚都会优等若干人而已。非乐育之本意。今者重新其屋。聚道内有志行才艺之士。为导率课学之计。玆用略定节目。以为永久遵行之地焉。
凡取士。不可不审。而今列邑既各选士。入校居斋。可知其入选者。为当邑之望也。是以。只令各邑守令于其选士中举荐。大邑校额十五人。则荐几人。中邑校额七人。则荐几人。小邑校额五人。则荐几人。俱定日期。会于营下。以为试取之地焉。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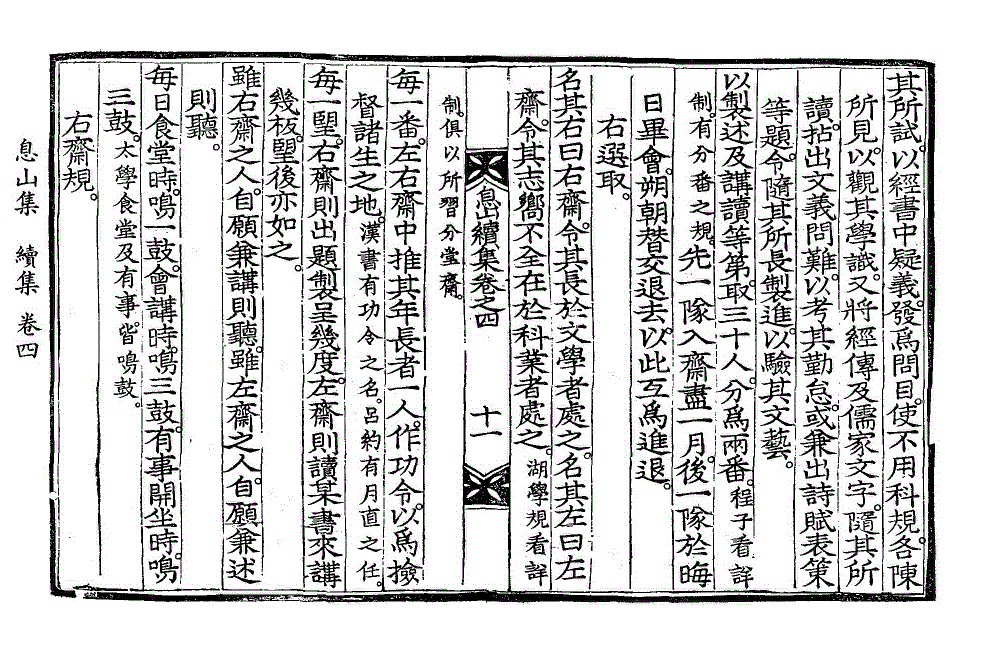 其所试。以经书中疑义。发为问目。使不用科规。各陈所见。以观其学识。又将经传及儒家文字。随其所读。拈出文义问难。以考其勤怠。或兼出诗赋表策等题。令随其所长制进。以验其文艺。
其所试。以经书中疑义。发为问目。使不用科规。各陈所见。以观其学识。又将经传及儒家文字。随其所读。拈出文义问难。以考其勤怠。或兼出诗赋表策等题。令随其所长制进。以验其文艺。以制述及讲读等第。取三十人。分为两番。(程子看详制。有分番之规。)先一队入斋尽一月。后一队于晦日毕会。朔朝替交退去。以此互为进退。
(右选取。)
名其右曰右斋。令其长于文学者处之。名其左曰左斋。令其志向不全在于科业者处之。(湖学规看详制。俱以所习分堂斋。)
每一番。左右斋中推其年长者一人。作功令。以为捡督诸生之地。(汉书有功令之名。吕约有月直之任。)
每一望。右斋则出题制呈几度。左斋则读某书来讲几板。望后亦如之。
虽右斋之人。自愿兼讲则听。虽左斋之人。自愿兼述则听。
每日食堂时。鸣一鼓。会讲时。鸣三鼓。有事开坐时。鸣三鼓。(太学食堂及有事。皆鸣鼓。)
(右斋规。)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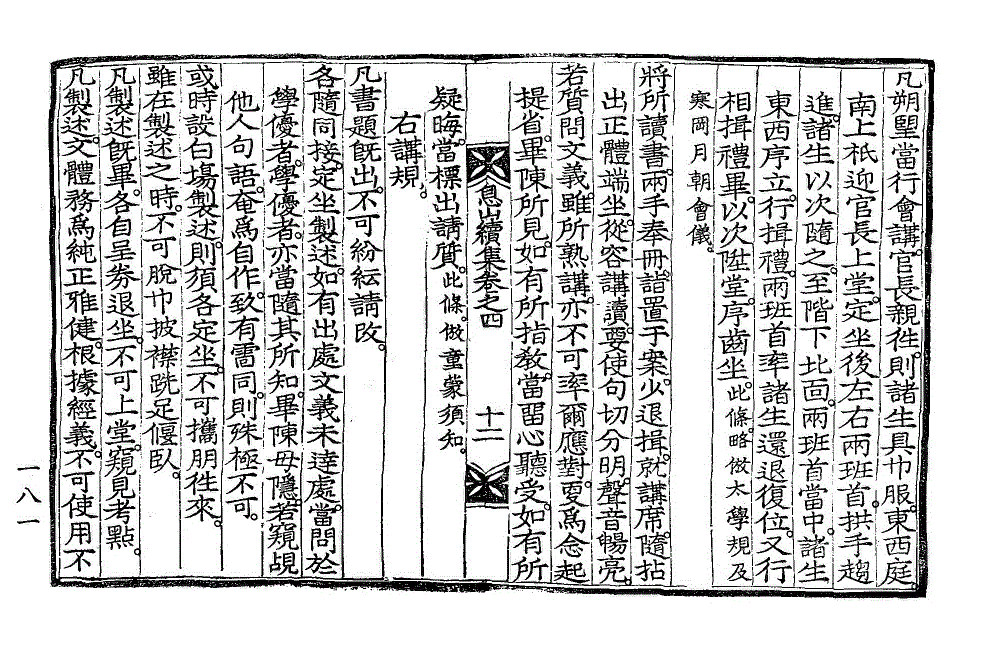 凡朔望当行会讲。官长亲往。则诸生具巾服。东西庭。南上祇迎官长上堂。定坐后左右两班首。拱手趋进。诸生以次随之。至阶下北面。两班首当中。诸生东西序立。行揖礼。两班首率诸生还退复位。又行相揖礼毕。以次升堂。序齿坐。(此条。略仿太学规及寒冈月朝会仪。)
凡朔望当行会讲。官长亲往。则诸生具巾服。东西庭。南上祇迎官长上堂。定坐后左右两班首。拱手趋进。诸生以次随之。至阶下北面。两班首当中。诸生东西序立。行揖礼。两班首率诸生还退复位。又行相揖礼毕。以次升堂。序齿坐。(此条。略仿太学规及寒冈月朝会仪。)将所读书。两手奉册。诣置于案。少退揖。就讲席。随拈出正体端坐。从容讲读。要使句切分明。声音畅亮。
若质问文义。虽所熟讲。亦不可率尔应对。更为念起提省。毕陈所见。如有所指教。当留心听受。如有所疑晦。当标出请质。(此条。仿童蒙须知。)
(右讲规。)
凡书题既出。不可纷纭请改。
各随同接。定坐制述。如有出处文义未达处。当问于学优者。学优者。亦当随其所知。毕陈毋隐。若窥觇他人句语。奄为自作。致有雷同。则殊极不可。
或时设白场制述。则须各定坐。不可携朋往来。
虽在制述之时。不可脱巾披襟跣足偃卧。
凡制述既毕。各自呈券退坐。不可上堂。窥见考点。
凡制述。文体务为纯正雅健。根据经义。不可使用不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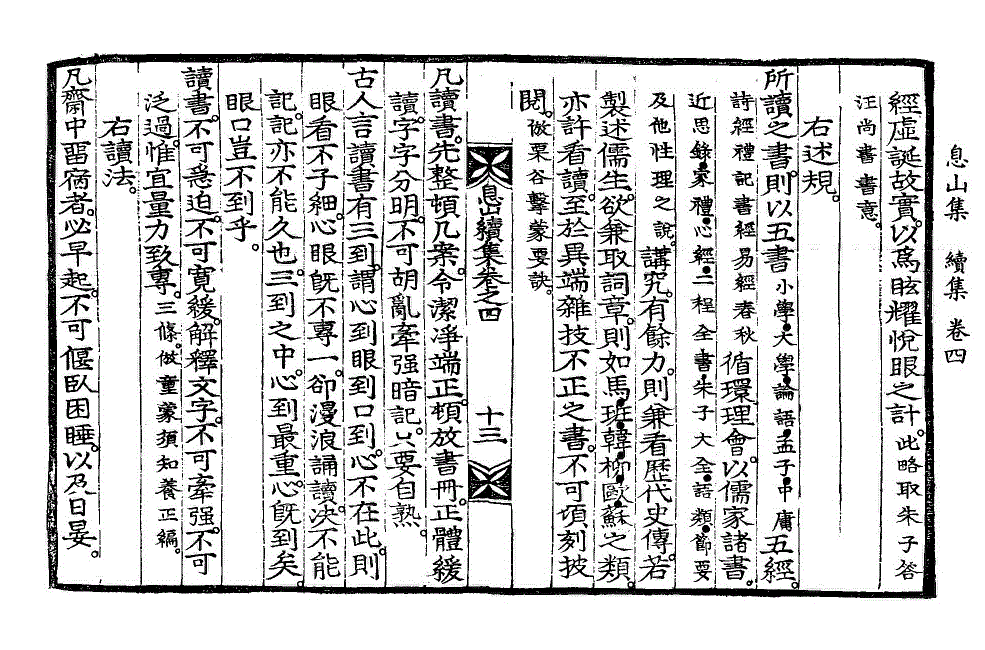 经虚诞故实。以为眩耀悦眼之计。(此略取朱子答汪尚书书意。)
经虚诞故实。以为眩耀悦眼之计。(此略取朱子答汪尚书书意。)(右述规。)
所读之书。则以五书(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诗经,礼记,书经,易经,春秋)循环理会。以儒家诸书。(近思录,家礼,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语类,节要及他性理之说。)讲究。有馀力。则兼看历代史传。若制述儒生。欲兼取词章。则如马,班,韩,柳,欧,苏之类。亦许看读。至于异端杂技不正之书。不可顷刻披阅。(仿栗谷击蒙要诀。)
凡读书。先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顿放书册。正体缓读。字字分明。不可胡乱牵强暗记。只要自熟。
古人言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重。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读书。不可急迫。不可宽缓。解释文字。不可牵强。不可泛过。惟宜量力致专。(三条。仿童蒙须知养正编。)
(右读法。)
凡斋中留宿者。必早起。不可偃卧困睡。以及日晏。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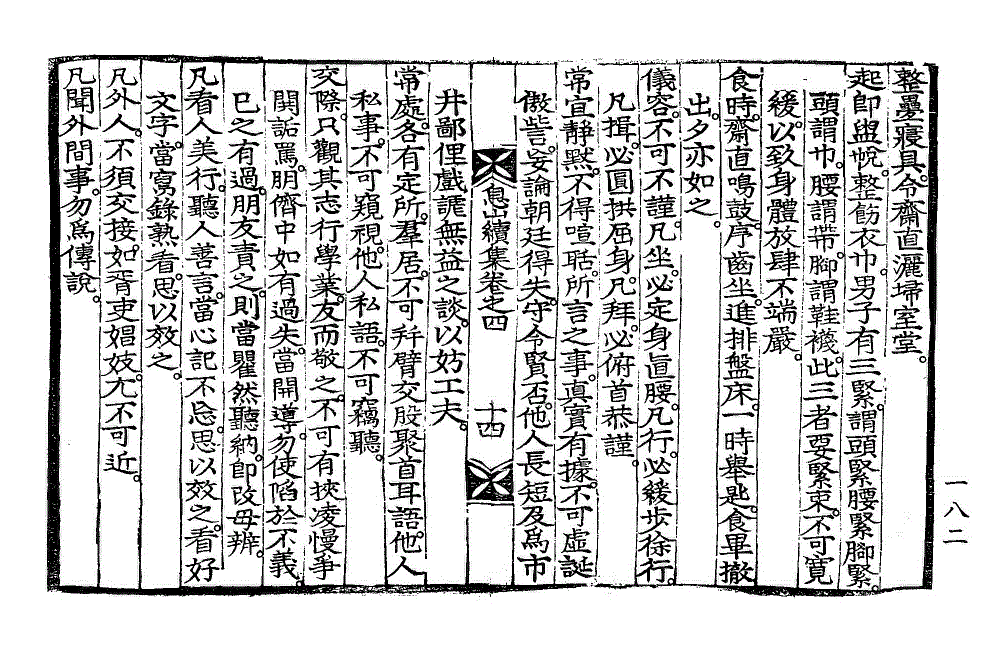 整叠寝具。令斋直洒埽室堂。
整叠寝具。令斋直洒埽室堂。起即盥帨。整饬衣巾。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巾。腰谓带。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缓。以致身体放肆不端严。
食时。斋直鸣鼓。序齿坐。进排盘床。一时举匙。食毕撤出。夕亦如之。
仪容。不可不谨。凡坐。必定身直腰。凡行。必缓步徐行。凡揖。必圆拱屈身。凡拜。必俯首恭谨。
常宜静默。不得喧聒。所言之事。真实有据。不可虚诞傲訾。妄论朝廷得失。守令贤否。他人长短及为市井鄙俚戏谑无益之谈。以妨工夫。
常处。各有定所。群居。不可并臂交股聚首耳语。他人私事。不可窥视。他人私语。不可窃听。
交际。只观其志行学业。友而敬之。不可有挟凌慢争閧诟骂。朋侪中如有过失。当开导。勿使陷于不义。己之有过。朋友责之。则当瞿然听纳。即改毋辨。
凡看人美行。听人善言。当心记不忘。思以效之。看好文字。当写录熟看。思以效之。
凡外人。不须交接。如胥吏娼妓。尤不可近。
凡闻外间事。勿为传说。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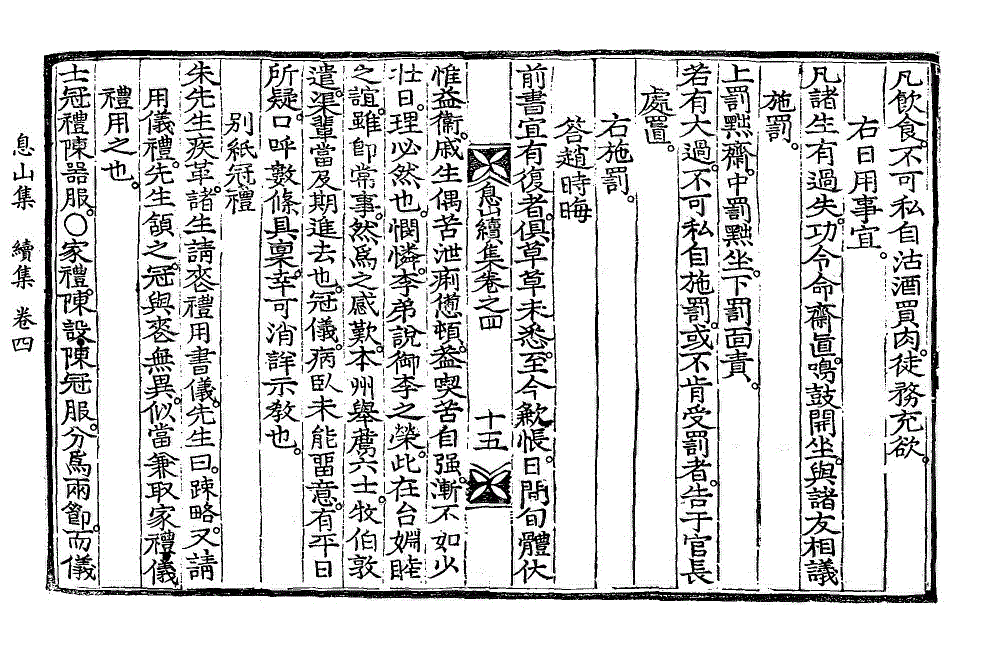 凡饮食。不可私自沽酒买肉。徒务充欲。
凡饮食。不可私自沽酒买肉。徒务充欲。(右日用事宜。)
凡诸生有过失。功令命斋直。鸣鼓开坐。与诸友相议施罚。
上罚黜斋。中罚黜坐。下罚面责。
若有大过。不可私自施罚。或不肯受罚者。告于官长处置。
(右施罚。)
答赵时晦
前书宜有复者。俱草草未悉。至今歉怅。日间旬体伏惟益卫。戚生偶苦泄痢惫顿。盖吃苦自强。渐不如少壮日。理必然也。悯怜。李弟说御李之荣。此在台姻睦之谊。虽即常事。然为之感叹。本州举荐六士。牧伯敦遣。渠辈当及期进去也。冠仪。病卧未能留意。有平日所疑。口呼数条具禀。幸可消详示教也。
别纸冠礼
朱先生疾革。诸生请丧礼用书仪。先生曰。疏略。又请用仪礼。先生颔之。冠与丧无异。似当兼取家礼,仪礼用之也。
士冠礼陈器服。○家礼。陈设,陈冠服。分为两节。而仪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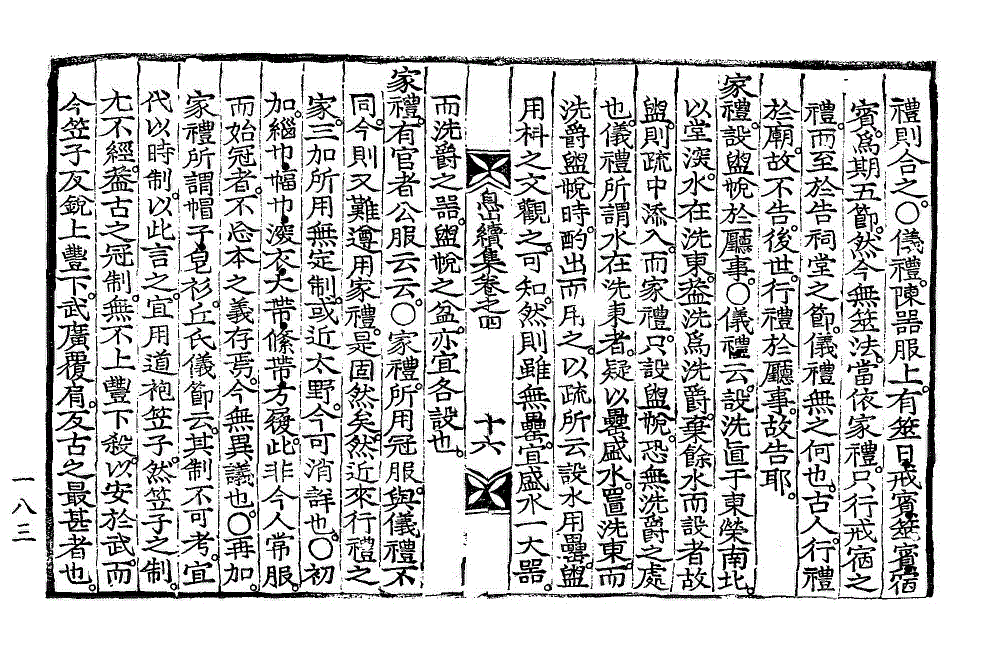 礼则合之。○仪礼。陈器服上。有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五节。然今无筮法。当依家礼。只行戒宿之礼。而至于告祠堂之节。仪礼无之何也。古人。行礼于庙。故不告。后世。行礼于厅事。故告耶。
礼则合之。○仪礼。陈器服上。有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五节。然今无筮法。当依家礼。只行戒宿之礼。而至于告祠堂之节。仪礼无之何也。古人。行礼于庙。故不告。后世。行礼于厅事。故告耶。家礼。设盥帨于厅事。○仪礼云。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盖洗为洗爵。弃馀水而设者故盥。则疏中添入。而家礼。只设盥帨。恐无洗爵之处也。仪礼所谓水在洗东者。疑以罍盛水。置洗东。而洗爵盥帨时。酌出而用之。以疏所云。设水用罍。盥用枓之文观之。可知。然则虽无罍。宜盛水一大器。而洗爵之器。盥帨之盆。亦宜各设也。
家礼。有官者公服云云。○家礼。所用冠服。与仪礼不同。今则又难遵用家礼。是固然矣。然近来行礼之家。三加所用无定制。或近太野。今可消详也。○初加。缁巾,幅巾,深衣,大带,绦带,方履。此非今人常服。而始冠者。不忘本之义存焉。今无异议也。○再加。家礼所谓帽子,皂衫。丘氏仪节云。其制不可考。宜代以时制。以此言之。宜用道袍笠子。然笠子之制。尤不经。盖古之冠制。无不上丰下杀。以安于武。而今笠子反锐上丰下。武广覆肩。反古之最甚者也。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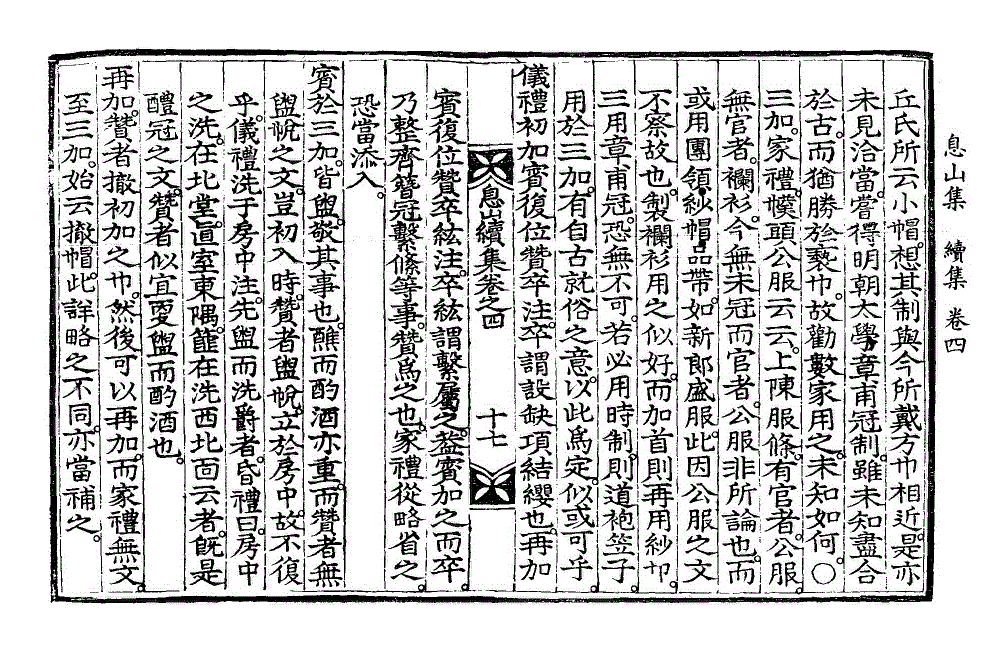 丘氏所云小帽。想其制与今所戴方巾相近。是亦未见洽当。尝得明朝太学章甫冠制。虽未知尽合于古。而犹胜于亵巾。故劝数家用之。未知如何。○三加。家礼。幞头公服云云。上陈服条。有官者。公服。无官者。襕衫。今无未冠而官者。公服非所论也。而或用团领,纱帽,品带。如新郎盛服。此因公服之文不察故也。制襕衫用之似好。而加首则再用纱巾。三用章甫冠。恐无不可。若必用时制。则道袍笠子。用于三加。有自古就俗之意。以此为定。似或可乎。
丘氏所云小帽。想其制与今所戴方巾相近。是亦未见洽当。尝得明朝太学章甫冠制。虽未知尽合于古。而犹胜于亵巾。故劝数家用之。未知如何。○三加。家礼。幞头公服云云。上陈服条。有官者。公服。无官者。襕衫。今无未冠而官者。公服非所论也。而或用团领,纱帽,品带。如新郎盛服。此因公服之文不察故也。制襕衫用之似好。而加首则再用纱巾。三用章甫冠。恐无不可。若必用时制。则道袍笠子。用于三加。有自古就俗之意。以此为定。似或可乎。仪礼初加宾复位赞卒注。卒谓设缺项结缨也。再加宾复位赞卒纮注。卒纮谓系属之。盖宾加之而卒。乃整齐簪冠系绦等事。赞为之也。家礼从略省之。恐当添入。
宾于三加。皆盥。敬其事也。醮而酌酒亦重。而赞者无盥帨之文。岂初入时。赞者盥帨。立于房中。故不复乎。仪礼洗于房中注。先盥而洗爵者。昏礼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东隅。篚在洗西北面云者。既是醴冠之文。赞者似宜更盥而酌酒也。
再加。赞者撤初加之巾。然后可以再加。而家礼无文。至三加。始云撤帽。此详略之不同。亦当补之。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4L 页
 醮。家礼。略荐脯。盖因书仪也。丘氏以为祝辞云。嘉荐令芳。不荐脯而谓之令芳。是为虚设。其言亦是。宜补荐脯之节也。
醮。家礼。略荐脯。盖因书仪也。丘氏以为祝辞云。嘉荐令芳。不荐脯而谓之令芳。是为虚设。其言亦是。宜补荐脯之节也。答赵时晦
窃伏惟念。我 圣祖仙驭。复出人世。臣民追感。可胜言哉。赵君与斋生奉书归。次第承悉。旬候震艮。一向珍卫。深慰区区。试士题目甚正。常谓科法猝难变通。今乃验。苟欲正之。亦在一转移间也。李生材质志趣俱可尚。但欠毅确意。每劝其凝定。而变化气质。亦未易。自此若蒙导率。使节其所长而益其所不足。至于成就。岂不幸甚。德和之兄名国春者。亦佳士。以年过课限。不入塾额。然断意名利。专心此事。不愧为德和之兄也。蔡,权二生。志操亦不凡。但所对似未甚简精。固宜不入于枰停也。全岭赤地之惨。振古所无。济一方生民之命。是台之责。刍牧之方。果有定算乎。窃闻以商山一隅为稍稔云。未知台何从而得之也。自咸过尚。路出俭湖大灌之下。负郭水耨。亦有不渴之溉。禾苗之秀。稍胜他处。往来见者。必以此为言。然以此较方百里之内。不及百之一也。日前。因外面塾士邀请。东西赴近百程。西则依峡。东则际水旱潦。两灾俱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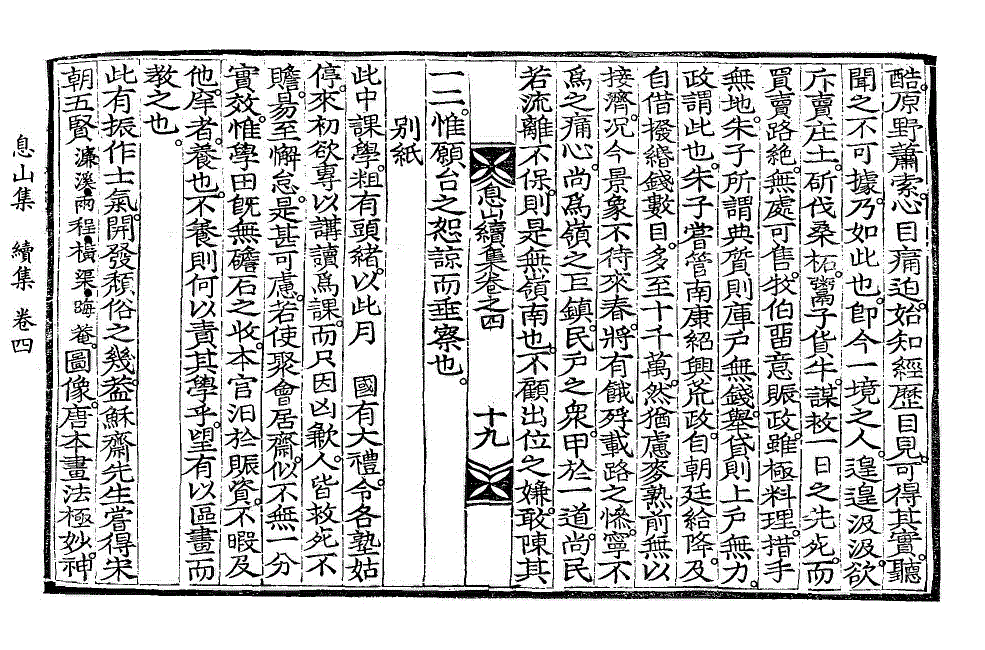 酷。原野萧索。心目痛迫。始知经历目见。可得其实。听闻之不可据。乃如此也。即今一境之人。遑遑汲汲。欲斥卖庄土。斫伐桑柘。鬻子货牛。谋救一日之先死。而买卖路绝。无处可售。牧伯留意赈政。虽极料理。措手无地。朱子所谓典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政谓此也。朱子尝管南康绍兴荒政。自朝廷给降。及自借拨缗钱数目。多至十千万。然犹虑麦熟前无以接济。况今景象不待来春。将有饿殍载路之惨。宁不为之痛心。尚为岭之巨镇。民户之众。甲于一道。尚民若流离不保。则是无岭南也。不顾出位之嫌。敢陈其一二。惟愿台之恕谅而垂察也。
酷。原野萧索。心目痛迫。始知经历目见。可得其实。听闻之不可据。乃如此也。即今一境之人。遑遑汲汲。欲斥卖庄土。斫伐桑柘。鬻子货牛。谋救一日之先死。而买卖路绝。无处可售。牧伯留意赈政。虽极料理。措手无地。朱子所谓典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政谓此也。朱子尝管南康绍兴荒政。自朝廷给降。及自借拨缗钱数目。多至十千万。然犹虑麦熟前无以接济。况今景象不待来春。将有饿殍载路之惨。宁不为之痛心。尚为岭之巨镇。民户之众。甲于一道。尚民若流离不保。则是无岭南也。不顾出位之嫌。敢陈其一二。惟愿台之恕谅而垂察也。别纸
此中课学。粗有头绪。以此月 国有大礼。令各塾姑停。来初欲专以讲读为课。而只因凶歉。人皆救死不赡。易至懈怠。是甚可虑。若使聚会居斋。似不无一分实效。惟学田既无䃫石之收。本官汩于赈资。不暇及他。庠者。养也。不养则何以责其学乎。望有以区画而教之也。
此有振作士气。开发颓俗之几。盖稣斋先生尝得宋朝五贤(濂溪,两程,横渠,晦庵。)图像。唐本画法极妙。神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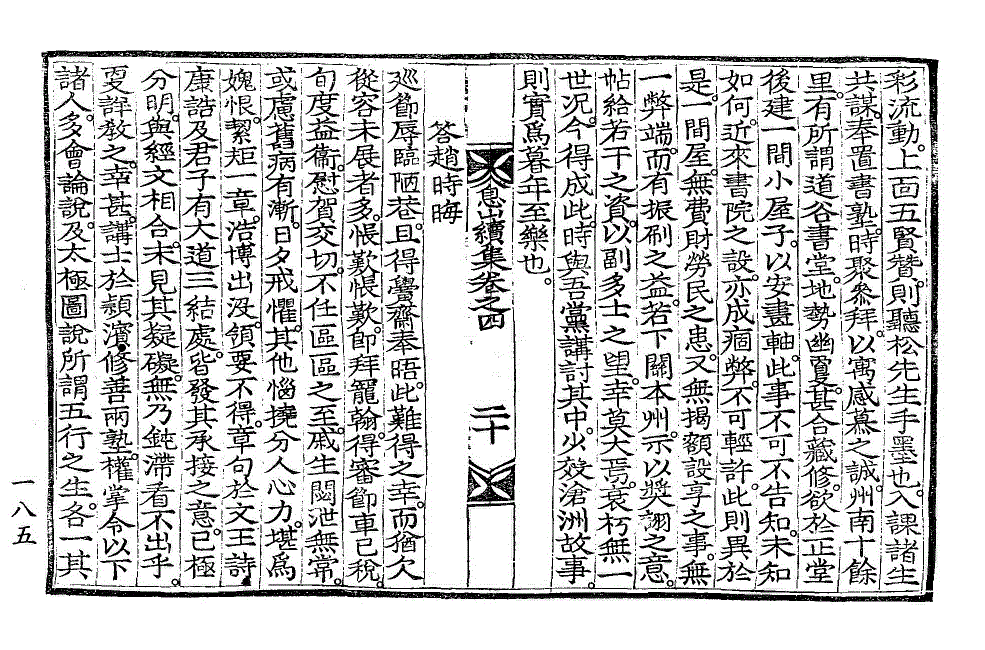 彩流动。上面五贤赞。则听松先生手墨也。入课诸生共谋。奉置书塾。时聚参拜。以寓感慕之诚。州南十馀里。有所谓道谷书堂。地势幽夐。甚合藏修。欲于正堂后建一间小屋子。以安画轴。此事不可不告知。未知如何。近来书院之设。亦成痼弊。不可轻许。此则异于是。一间屋。无费财劳民之患。又无揭额设享之事。无一弊端。而有振刷之益。若下关本州。示以奖诩之意。帖给若干之资。以副多士之望。幸莫大焉。衰朽无一世况。今得成此。时与吾党讲讨其中。少效沧洲故事。则实为暮年至乐也。
彩流动。上面五贤赞。则听松先生手墨也。入课诸生共谋。奉置书塾。时聚参拜。以寓感慕之诚。州南十馀里。有所谓道谷书堂。地势幽夐。甚合藏修。欲于正堂后建一间小屋子。以安画轴。此事不可不告知。未知如何。近来书院之设。亦成痼弊。不可轻许。此则异于是。一间屋。无费财劳民之患。又无揭额设享之事。无一弊端。而有振刷之益。若下关本州。示以奖诩之意。帖给若干之资。以副多士之望。幸莫大焉。衰朽无一世况。今得成此。时与吾党讲讨其中。少效沧洲故事。则实为暮年至乐也。答赵时晦
巡节辱临陋巷。且得黉斋奉晤。此难得之幸。而犹欠从容未展者多。怅叹怅叹。即拜宠翰。得审节车已税。旬度益卫。慰贺交切。不任区区之至。戚生閟泄无常。或虑旧病有渐。日夕戒惧。其他恼挠分人心力。堪为愧恨。絜矩一章。浩博出没。领要不得。章句于文王诗,康诰及君子有大道三结处。皆发其承接之意。已极分明。与经文相合。未见其疑碍。无乃钝滞看不出乎。更详教之。幸甚。讲士于颖滨,修善两塾。权掌令以下诸人。多会论说。及太极图说所谓五行之生。各一其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6H 页
 性。或以气质之性言之。或以本然之性言之。又论思意先后。或以为思先或以为意先。鄙陋略有所答。性字以本性言者。改作气质者有之。而思意先后。竟未归一。如蒙剖判之教。可作士林公案也。壁韵要诸人续和。待收合。可以仰尘崇览。鄙陋率尔强缀数语。又因塾会。示诸生有作。今并录呈。可博一粲也。
性。或以气质之性言之。或以本然之性言之。又论思意先后。或以为思先或以为意先。鄙陋略有所答。性字以本性言者。改作气质者有之。而思意先后。竟未归一。如蒙剖判之教。可作士林公案也。壁韵要诸人续和。待收合。可以仰尘崇览。鄙陋率尔强缀数语。又因塾会。示诸生有作。今并录呈。可博一粲也。答赵时晦
两度惠书。得泻鄙吝。荷赐甚大。仍审旬候增福。慰亦至矣。戚生日寒来。苦业。依旧寻蜗壳里破产计。成未成。俱关心无可言者。絜矩章句。反覆所教。略悉只眼独造。若徒谨守笃信。遽未能及此也。然更勘上下数节发挥语势。所谓双行寄边者。未见其然。盖文王诗注中。一心字为诸节得失之纲领。好恶也财用也用舍也。其能絜矩与不能者。只因心之存不存。而得失相反。以心为万事之矩也。第一节言能存是心。而下二节皆云又又者。谓因财货用舍。而申之以能絜矩与不能者得失云尔。以此言之。所谓双行寄边。非所虑矣。如何如何。思意之辨。前答诸君书云。诗曰思无邪。程子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此俱以心之初发处言。朱子曰。意者。主张要恁地。栗谷曰。意者。缘情计较。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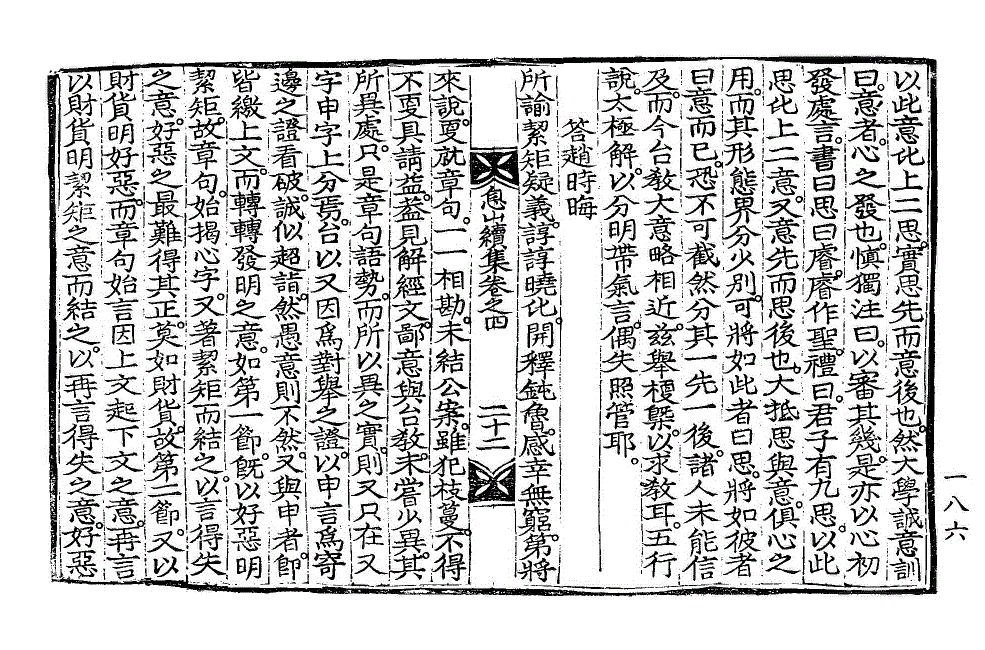 以此意比上二思。实思先而意后也。然大学诚意训曰。意者。心之发也。慎独注曰。以审其几。是亦以心初发处言。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礼曰。君子有九思。以此思比上二意。又意先而思后也。大抵思与意。俱心之用。而其形态界分少别。可将如此者曰思。将如彼者曰意而已。恐不可截然分其一先一后。诸人未能信及。而今台教大意略相近。玆举梗槩。以求教耳。五行说。太极解。以分明带气言。偶失照管耶。
以此意比上二思。实思先而意后也。然大学诚意训曰。意者。心之发也。慎独注曰。以审其几。是亦以心初发处言。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礼曰。君子有九思。以此思比上二意。又意先而思后也。大抵思与意。俱心之用。而其形态界分少别。可将如此者曰思。将如彼者曰意而已。恐不可截然分其一先一后。诸人未能信及。而今台教大意略相近。玆举梗槩。以求教耳。五行说。太极解。以分明带气言。偶失照管耶。答赵时晦
所谕絜矩疑义。谆谆晓比。开释钝鲁。感幸无穷。第将来说。更就章句。一一相勘。未结公案。虽犯枝蔓。不得不更具请益。盖见解经文。鄙意与台教。未尝少异。其所异处。只是章句语势。而所以异之实。则又只在又字申字上分焉。台以又因为对举之證。以申言为寄边之證看破。诚似超诣。然愚意则不然。又与申者。即皆缴上文。而转转发明之意。如第一节。既以好恶明絜矩。故章句。始揭心字。又著絜矩而结之。以言得失之意。好恶之最难得其正。莫如财货。故第二节。又以财货明好恶。而章句始言因上文起下文之意。再言以财货明絜矩之意而结之。以再言得失之意。好恶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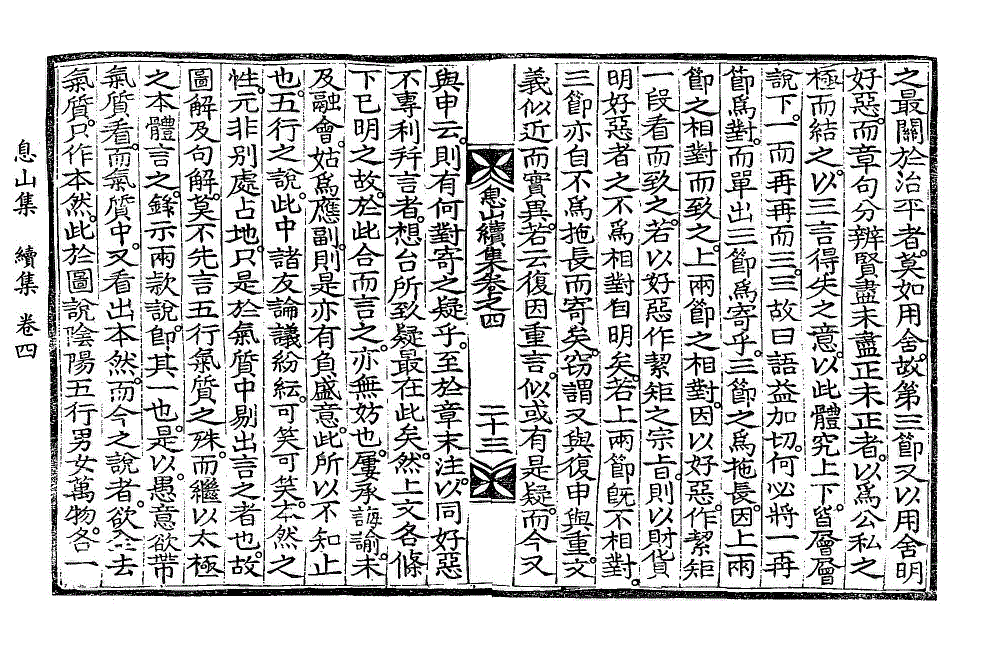 之最关于治平者。莫如用舍。故第三节又以用舍明好恶。而章句分辨贤尽未尽正未正者。以为公私之极而结之。以三言得失之意。以此体究上下。皆层层说下。一而再再而三。三故曰语益加切。何必将一再节为对。而单出三节为寄乎。三节之为拖长。因上两节之相对而致之。上两节之相对。因以好恶。作絜矩一段看而致之。若以好恶作絜矩之宗旨。则以财货明好恶者之不为相对自明矣。若上两节既不相对。三节亦自不为拖长而寄矣。窃谓又与复申与重。文义似近而实异。若云复因重言。似或有是疑。而今又与申云。则有何对寄之疑乎。至于章末注。以同好恶不专利并言者。想台所致疑最在此矣。然上文各条下已明之故。于此合而言之。亦无妨也。屡承诲谕。未及融会。姑为应副。则是亦有负盛意。此所以不知止也。五行之说。此中诸友论议纷纭。可笑可笑。本然之性。元非别处占地。只是于气质中剔出言之者也。故图解及句解。莫不先言五行气质之殊。而继以太极之本体言之。录示两款说。即其一也。是以。愚意欲带气质看。而气质中。又看出本然。而今之说者。欲全去气质。只作本然。此于图说阴阳五行男女万物。各一
之最关于治平者。莫如用舍。故第三节又以用舍明好恶。而章句分辨贤尽未尽正未正者。以为公私之极而结之。以三言得失之意。以此体究上下。皆层层说下。一而再再而三。三故曰语益加切。何必将一再节为对。而单出三节为寄乎。三节之为拖长。因上两节之相对而致之。上两节之相对。因以好恶。作絜矩一段看而致之。若以好恶作絜矩之宗旨。则以财货明好恶者之不为相对自明矣。若上两节既不相对。三节亦自不为拖长而寄矣。窃谓又与复申与重。文义似近而实异。若云复因重言。似或有是疑。而今又与申云。则有何对寄之疑乎。至于章末注。以同好恶不专利并言者。想台所致疑最在此矣。然上文各条下已明之故。于此合而言之。亦无妨也。屡承诲谕。未及融会。姑为应副。则是亦有负盛意。此所以不知止也。五行之说。此中诸友论议纷纭。可笑可笑。本然之性。元非别处占地。只是于气质中剔出言之者也。故图解及句解。莫不先言五行气质之殊。而继以太极之本体言之。录示两款说。即其一也。是以。愚意欲带气质看。而气质中。又看出本然。而今之说者。欲全去气质。只作本然。此于图说阴阳五行男女万物。各一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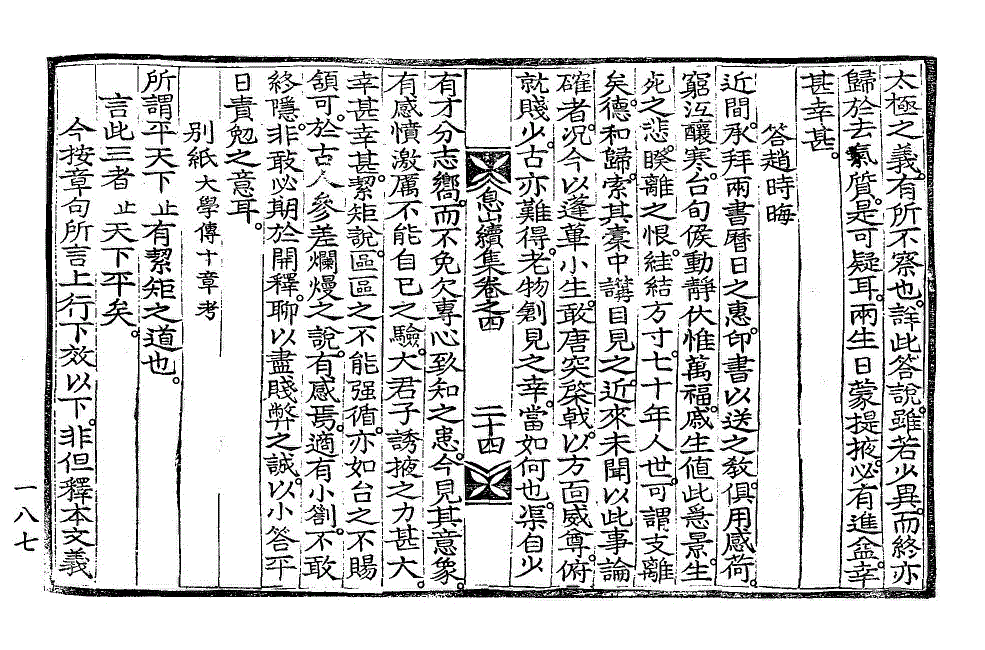 太极之义。有所不察也。详此答说。虽若少异。而终亦归于去气质。是可疑耳。两生日蒙提掖。必有进益。幸甚幸甚。
太极之义。有所不察也。详此答说。虽若少异。而终亦归于去气质。是可疑耳。两生日蒙提掖。必有进益。幸甚幸甚。答赵时晦
近间。承拜两书历日之惠。印书以送之教。俱用感荷。穷冱酿寒。台旬候动静伏惟万福。戚生值此急景。生死之悲。睽离之恨。絓结方寸。七十年人世。可谓支离矣。德和归。索其橐中讲目见之。近来未闻以此事论确者。况今以蓬荜小生。敢唐突棨戟。以方面威尊。俯就贱少。古亦难得。老物创见之幸。当如何也。渠自少有才分志向。而不免欠专心致知之患。今见其意象。有感愤激厉不能自已之验。大君子诱掖之力甚大。幸甚幸甚。絜矩说。区区之不能强循。亦如台之不赐颔可。于古人参差烂熳之说。有感焉。适有小劄。不敢终隐。非敢必期于开释。聊以尽贱弊之诚。以小答平日责勉之意耳。
别纸(大学传十章考)
所谓平天下(止)有絜矩之道也。
言此三者(止)天下平矣。
今按章句所言上行下效以下。非但释本文义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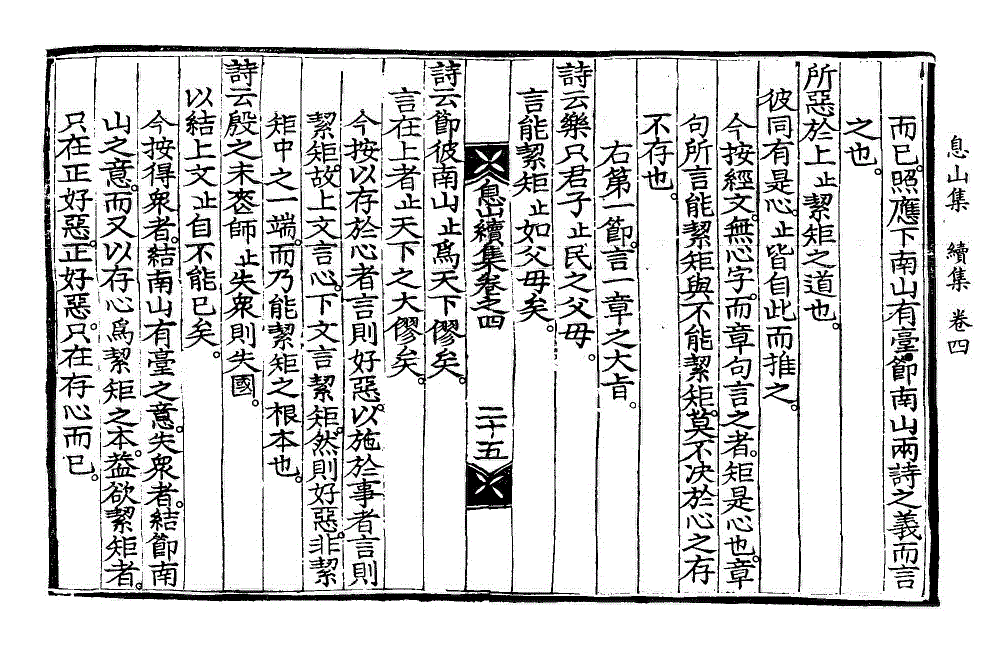 而已。照应下南山有台,节南山两诗之义而言之也。
而已。照应下南山有台,节南山两诗之义而言之也。所恶于上(止)絜矩之道也。
彼同有是心(止)皆自此而推之。
今按经文。无心字。而章句言之者。矩是心也。章句所言能絜矩与不能絜矩。莫不决于心之存不存也。
右第一节。言一章之大旨。
诗云乐只君子(止)民之父母。
言能絜矩(止)如父母矣。
诗云节彼南山(止)为天下僇矣。
言在上者(止)天下之大僇矣。
今按以存于心者言则好恶。以施于事者言则絜矩。故上文言心。下文言絜矩。然则好恶。非絜矩中之一端。而乃能絜矩之根本也。
诗云殷之未丧师(止)失众则失国。
以结上文(止)自不能已矣。
今按得众者。结南山有台之意。失众者。结节南山之意。而又以存心为絜矩之本。盖欲絜矩者。只在正好恶。正好恶。只在存心而已。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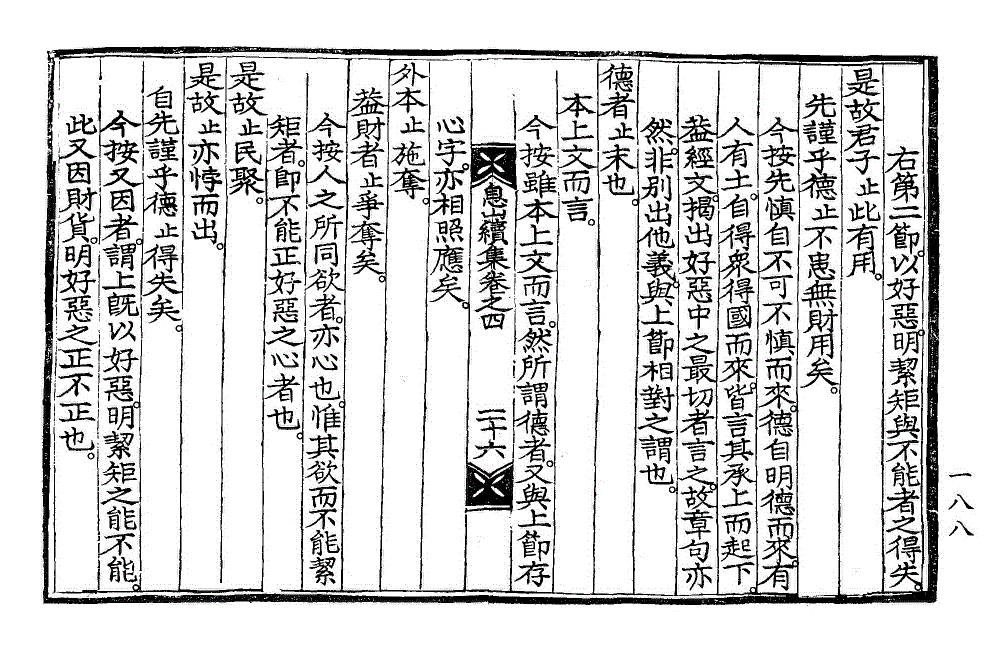 右第二节。以好恶。明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
右第二节。以好恶。明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是故君子(止)此有用。
先谨乎德(止)不患无财用矣。
今按先慎自不可不慎而来。德自明德而来。有人有土。自得众得国而来。皆言其承上而起下。盖经文。揭出好恶中之最切者言之。故章句亦然。非别出他义。与上节相对之谓也。
德者(止)末也。
本上文而言。
今按虽本上文而言。然所谓德者。又与上节存心字。亦相照应矣。
外本(止)施夺。
盖财者(止)争夺矣。
今按人之所同欲者。亦心也。惟其欲而不能絜矩者。即不能正好恶之心者也。
是故(止)民聚。
是故(止)亦悖而出。
自先谨乎德(止)得失矣。
今按又因者。谓上既以好恶。明絜矩之能不能。此又因财货。明好恶之正不正也。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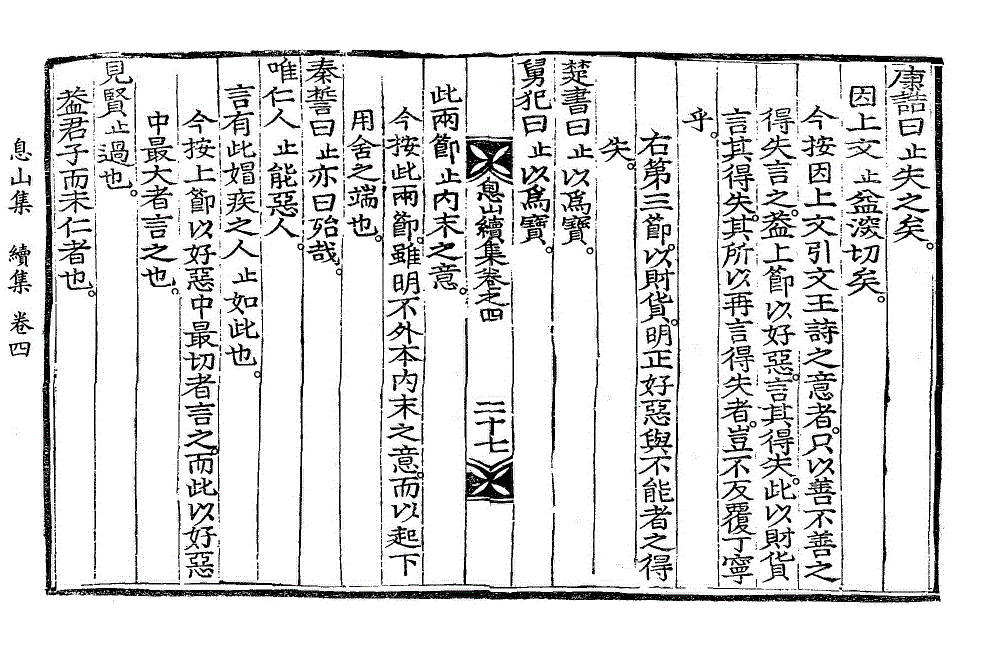 康诰曰(止)失之矣。
康诰曰(止)失之矣。因上文(止)益深切矣。
今按因上文引文王诗之意者。只以善不善之得失言之。盖上节以好恶。言其得失。此以财货言其得失。其所以再言得失者。岂不反覆丁宁乎。
右第三节。以财货。明正好恶与不能者之得失。
楚书曰(止)以为宝。
舅犯曰(止)以为宝。
此两节(止)内末之意。
今按此两节。虽明不外本内末之意。而以起下用舍之端也。
秦誓曰(止)亦曰殆哉。
唯仁人(止)能恶人。
言有此媢疾之人(止)如此也。
今按上节以好恶中最切者言之。而此以好恶中最大者言之也。
见贤(止)过也。
盖君子而未仁者也。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89L 页
 好人之所恶(止)必逮夫身。
好人之所恶(止)必逮夫身。又皆以(止)节南山之意。
今按秦誓分言好恶之正不正。其下文。言好恶之得其正。又下两文。言好恶之未尽与拂好恶之性者。盖上。以财货。明好恶之正不正。此以用舍。明好恶之正不正。故云申言也。
是故君子(止)以失之。
因上所引(止)决矣。
今按得失字。自文王诗康诰两节而来。故曰三言。
右第四节。以用舍。明正好恶与不能者之得失。
生财有大道(止)恒足矣。
自此(止)皆一意也。
今按自此至终篇。合财货用舍而言之。故云一意。与经文排布之意。未尝有异也。
右第五节。合财货用舍。明好恶得失之馀意。云峰胡氏。分一章为八节。以细节而言也。此以章句所分者为节。以见章句之无背于经文也。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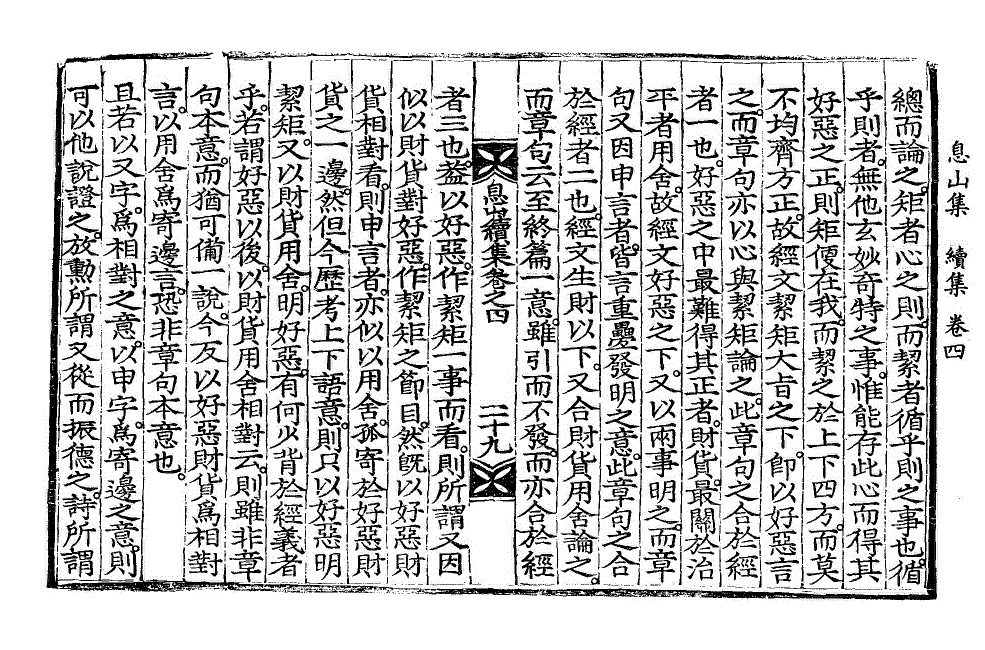 总而论之。矩者心之则。而絜者循乎则之事也。循乎则者。无他玄妙奇特之事。惟能存此心而得其好恶之正。则矩便在我。而絜之于上下四方。而莫不均齐方正。故经文絜矩大旨之下。即以好恶言之。而章句亦以心与絜矩论之。此章句之合于经者一也。好恶之中最难得其正者。财货。最关于治平者用舍。故经文好恶之下。又以两事明之。而章句又因申言者。皆言重叠发明之意。此章句之合于经者二也。经文生财以下。又合财货用舍论之。而章句云至终篇一意。虽引而不发。而亦合于经者三也。盖以好恶。作絜矩一事而看。则所谓又因似以财货对好恶。作絜矩之节目。然既以好恶财货相对看。则申言者。亦似以用舍。孤寄于好恶财货之一边。然但今历考上下语意。则只以好恶明絜矩。又以财货用舍。明好恶。有何少背于经义者乎。若谓好恶以后。以财货用舍相对云。则虽非章句本意。而犹可备一说。今反以好恶财货为相对言。以用舍为寄边言。恐非章句本意也。
总而论之。矩者心之则。而絜者循乎则之事也。循乎则者。无他玄妙奇特之事。惟能存此心而得其好恶之正。则矩便在我。而絜之于上下四方。而莫不均齐方正。故经文絜矩大旨之下。即以好恶言之。而章句亦以心与絜矩论之。此章句之合于经者一也。好恶之中最难得其正者。财货。最关于治平者用舍。故经文好恶之下。又以两事明之。而章句又因申言者。皆言重叠发明之意。此章句之合于经者二也。经文生财以下。又合财货用舍论之。而章句云至终篇一意。虽引而不发。而亦合于经者三也。盖以好恶。作絜矩一事而看。则所谓又因似以财货对好恶。作絜矩之节目。然既以好恶财货相对看。则申言者。亦似以用舍。孤寄于好恶财货之一边。然但今历考上下语意。则只以好恶明絜矩。又以财货用舍。明好恶。有何少背于经义者乎。若谓好恶以后。以财货用舍相对云。则虽非章句本意。而犹可备一说。今反以好恶财货为相对言。以用舍为寄边言。恐非章句本意也。且若以又字。为相对之意。以申字。为寄边之意。则可以他说證之。放勋所谓又从而振德之。诗所谓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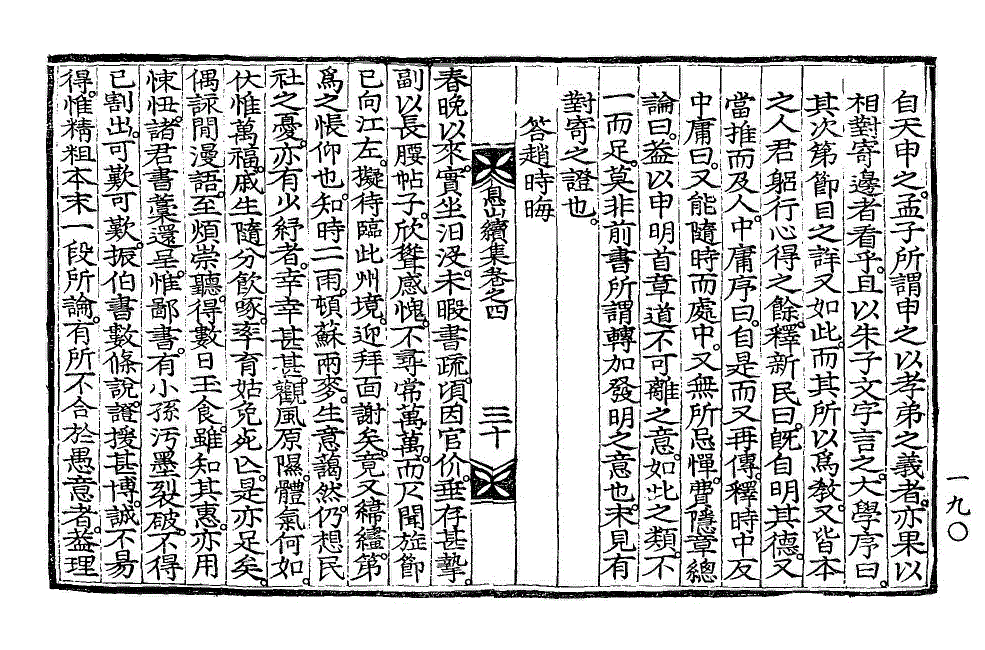 自天申之。孟子所谓申之以孝弟之义者。亦果以相对寄边者看乎。且以朱子文字言之。大学序曰。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释新民曰。既自明其德。又当推而及人。中庸序曰。自是而又再传。释时中反中庸曰。又能随时而处中。又无所忌惮。费隐章总论曰。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莫非前书所谓转加发明之意也。未见有对寄之證也。
自天申之。孟子所谓申之以孝弟之义者。亦果以相对寄边者看乎。且以朱子文字言之。大学序曰。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释新民曰。既自明其德。又当推而及人。中庸序曰。自是而又再传。释时中反中庸曰。又能随时而处中。又无所忌惮。费隐章总论曰。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莫非前书所谓转加发明之意也。未见有对寄之證也。答赵时晦
春晚以来。实坐汩没。未暇书疏。顷因官价。垂存甚挚。副以长腰帖子。欣耸感愧。不寻常万万。而仄闻旌节已向江左。拟待临此州境。迎拜面谢矣。竟又纬繣。第为之怅仰也。知时二雨。顿苏两麦。生意蔼然。仍想民社之忧。亦有少纾者。幸幸甚甚。观风原隰。体气何如。伏惟万福。戚生随分饮啄。率育姑免死亡。是亦足矣。偶咏閒漫语。至烦崇听。得数日玉食。虽知其惠。亦用悚忸。诸君书稿还呈。惟鄙书。有小孙污墨裂破。不得已割出。可叹可叹。振伯书数条说。證援甚博。诚不易得。惟精粗本末一段所论。有所不合于愚意者。盖理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91H 页
 与气虽混合无间。而有体用之分焉。主宰运行之异焉。若断之曰都无彼此云。则何以辨别其实也。况曰无彼此。则是以理气作一彼一此而无之也。一彼一此。则理气太分析。无之则理气太混沦。台教所谓生硬。不但在于言语之间也。然台教曰。主熊说则上下文句绝为一例。主栗说则上下文句绝为异例。抑未知栗谷本意果如是乎。窃意无论精粗本末。气之所在莫不有太极之理在其中。故曰无彼此。彼此字。以精粗言。而非以理气言也。如中庸愚夫愚妇之所知所能。是费之小者。圣人之所不知所不能。是费之大者。而莫不有所以然之理。所谓隐也。此与无彼此之说。有所相发。然则虽主栗说。其句绝亦与熊无异。然后方稳。而惟其义迥别也。若如台教作异例句绝。则似以太极别占地位。分排于阴阳五行。而无彼此者。然其解无彼此之义则当矣。而于理气本然之妙。似未甚端的。此所以敢疑而请益者。如何如何。
与气虽混合无间。而有体用之分焉。主宰运行之异焉。若断之曰都无彼此云。则何以辨别其实也。况曰无彼此。则是以理气作一彼一此而无之也。一彼一此。则理气太分析。无之则理气太混沦。台教所谓生硬。不但在于言语之间也。然台教曰。主熊说则上下文句绝为一例。主栗说则上下文句绝为异例。抑未知栗谷本意果如是乎。窃意无论精粗本末。气之所在莫不有太极之理在其中。故曰无彼此。彼此字。以精粗言。而非以理气言也。如中庸愚夫愚妇之所知所能。是费之小者。圣人之所不知所不能。是费之大者。而莫不有所以然之理。所谓隐也。此与无彼此之说。有所相发。然则虽主栗说。其句绝亦与熊无异。然后方稳。而惟其义迥别也。若如台教作异例句绝。则似以太极别占地位。分排于阴阳五行。而无彼此者。然其解无彼此之义则当矣。而于理气本然之妙。似未甚端的。此所以敢疑而请益者。如何如何。与赵时晦
退溪言行通录刊役已始。此乃台右文中一事甚盛。幸甚幸甚。江左闻士。莫不来会。参听其绪馀。亦索居人不易得者。但通录最下附以年谱。区区窃谓年谱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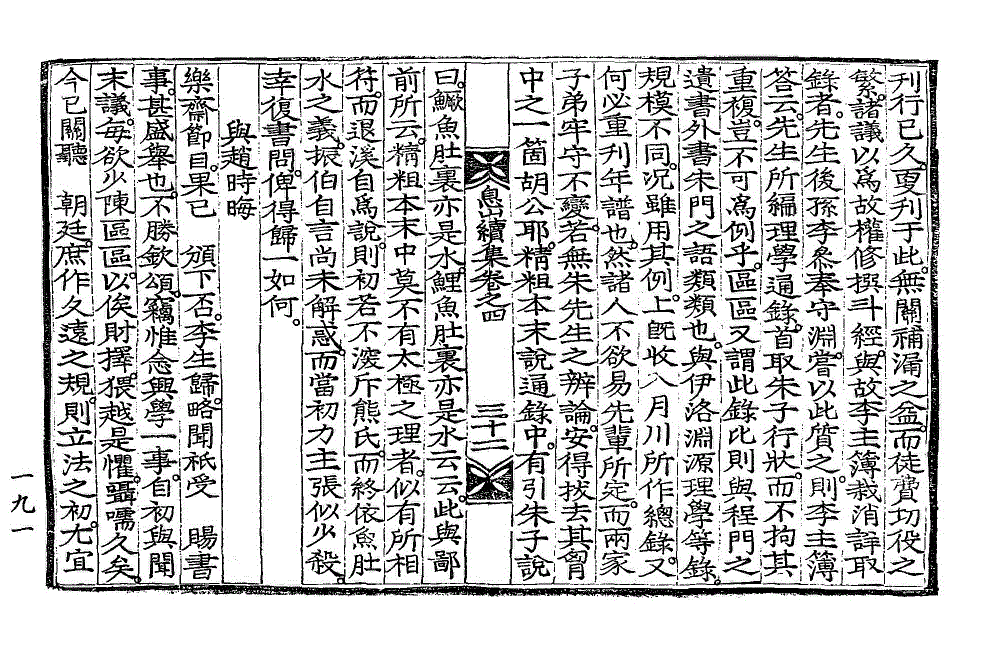 刊行已久。更刊于此。无关补漏之益。而徒费功役之繁。诸议以为故权修撰斗经。与故李主簿栽消详取录者。先生后孙李参奉守渊。尝以此质之。则李主簿答云。先生所编理学通录。首取朱子行状。而不拘其重复。岂不可为例乎。区区又谓此录比则与程门之遗书外书朱门之语类类也。与伊洛渊源理学等录。规模不同。况虽用其例。上既收入月川所作总录。又何必重刊年谱也。然诸人不欲易先辈所定。而两家子弟牢守不变。若无朱先生之辨论。安得拔去其胸中之一个胡公耶。精粗本末说通录中。有引朱子说曰。鳜鱼肚里亦是水。鲤鱼肚里亦是水云云。此与鄙前所云。精粗本末中莫不有太极之理者。似有所相符。而退溪自为说。则初若不深斥熊氏。而终依鱼肚水之义。振伯自言尚未解惑。而当初力主张似少杀。幸复书问。俾得归一如何。
刊行已久。更刊于此。无关补漏之益。而徒费功役之繁。诸议以为故权修撰斗经。与故李主簿栽消详取录者。先生后孙李参奉守渊。尝以此质之。则李主簿答云。先生所编理学通录。首取朱子行状。而不拘其重复。岂不可为例乎。区区又谓此录比则与程门之遗书外书朱门之语类类也。与伊洛渊源理学等录。规模不同。况虽用其例。上既收入月川所作总录。又何必重刊年谱也。然诸人不欲易先辈所定。而两家子弟牢守不变。若无朱先生之辨论。安得拔去其胸中之一个胡公耶。精粗本末说通录中。有引朱子说曰。鳜鱼肚里亦是水。鲤鱼肚里亦是水云云。此与鄙前所云。精粗本末中莫不有太极之理者。似有所相符。而退溪自为说。则初若不深斥熊氏。而终依鱼肚水之义。振伯自言尚未解惑。而当初力主张似少杀。幸复书问。俾得归一如何。与赵时晦
乐斋节目。果已 颁下否。李生归。略闻祇受 赐书事。甚盛举也。不胜钦颂。窃惟念兴学一事。自初与闻末议。每欲少陈区区。以俟财择。猥越是惧。嗫嚅久矣。今已关听 朝廷。庶作久远之规。则立法之初。尤宜
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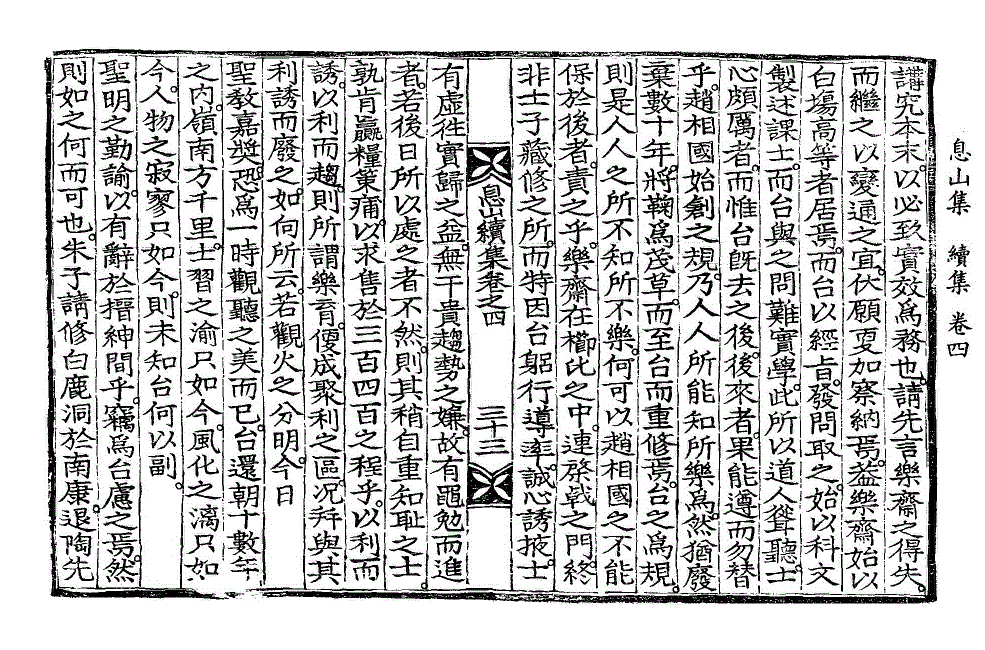 讲究本末。以必致实效为务也。请先言乐斋之得失。而继之以变通之宜。伏愿更加察纳焉。盖乐斋始以白场高等者居焉。而台以经旨。发问取之。始以科文制述课士。而台与之问难实学。此所以道人耸听。士心颇厉者。而惟台既去之后。后来者。果能遵而勿替乎。赵相国始创之规。乃人人所能知所乐为。然犹废弃数十年。将鞠为茂草。而至台而重修焉。台之为规。则是人人之所不知所不乐。何可以赵相国之不能保于后者。责之乎。乐斋在栉比之中。连棨戟之门。终非士子藏修之所。而特因台躬行导率。诚心诱掖。士有虚往实归之益。无干贵趋势之嫌。故有黾勉而进者。若后日所以处之者不然。则其稍自重知耻之士。孰肯赢粮策痡。以求售于三百四百之程乎。以利而诱。以利而趋。则所谓乐育。便成聚利之区。况并与其利诱而废之。如向所云。若观火之分明。今日 圣教嘉奖。恐为一时观听之美而已。台还朝十数年之内。岭南方千里。士习之渝只如今。风化之漓只如今。人物之寂寥只如今。则未知台何以副。 圣明之勤谕。以有辞于搢绅间乎。窃为台虑之焉。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朱子请修白鹿洞于南康。退陶先
讲究本末。以必致实效为务也。请先言乐斋之得失。而继之以变通之宜。伏愿更加察纳焉。盖乐斋始以白场高等者居焉。而台以经旨。发问取之。始以科文制述课士。而台与之问难实学。此所以道人耸听。士心颇厉者。而惟台既去之后。后来者。果能遵而勿替乎。赵相国始创之规。乃人人所能知所乐为。然犹废弃数十年。将鞠为茂草。而至台而重修焉。台之为规。则是人人之所不知所不乐。何可以赵相国之不能保于后者。责之乎。乐斋在栉比之中。连棨戟之门。终非士子藏修之所。而特因台躬行导率。诚心诱掖。士有虚往实归之益。无干贵趋势之嫌。故有黾勉而进者。若后日所以处之者不然。则其稍自重知耻之士。孰肯赢粮策痡。以求售于三百四百之程乎。以利而诱。以利而趋。则所谓乐育。便成聚利之区。况并与其利诱而废之。如向所云。若观火之分明。今日 圣教嘉奖。恐为一时观听之美而已。台还朝十数年之内。岭南方千里。士习之渝只如今。风化之漓只如今。人物之寂寥只如今。则未知台何以副。 圣明之勤谕。以有辞于搢绅间乎。窃为台虑之焉。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朱子请修白鹿洞于南康。退陶先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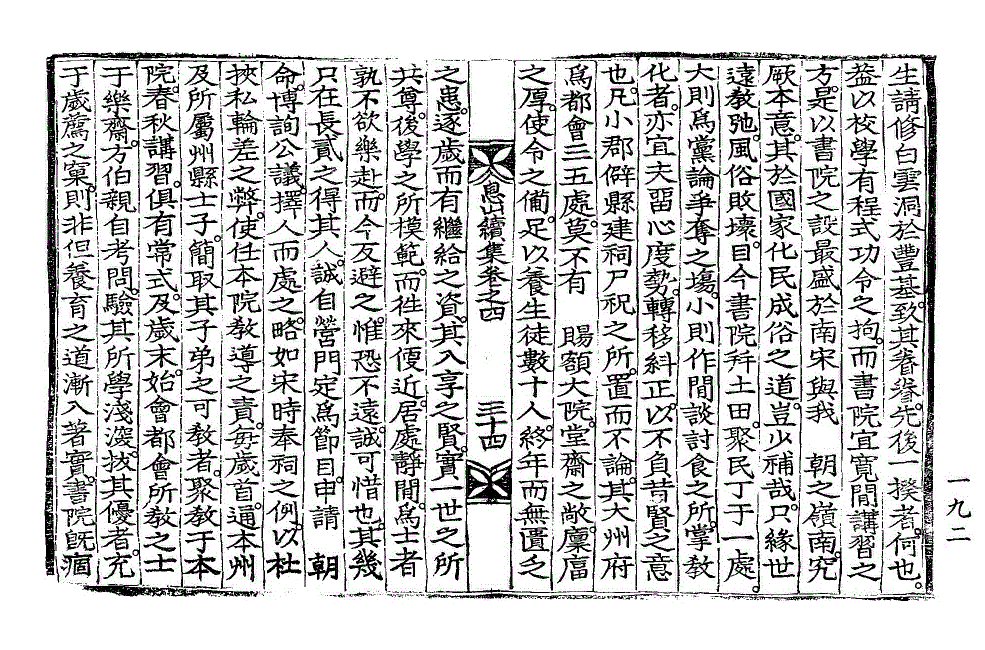 生请修白云洞于丰基。致其眷眷。先后一揆者。何也。盖以校学有程式功令之拘。而书院宜宽閒讲习之方。是以书院之设最盛于南宋与我 朝之岭南。究厥本意。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道。岂少补哉。只缘世远教弛。风俗败坏。目今书院并土田。聚民丁于一处。大则为党论争夺之场。小则作閒谈讨食之所。掌教化者。亦宜夫留心度势。转移纠正。以不负昔贤之意也。凡小郡僻县建祠尸祝之所。置而不论。其大州府为都会三五处。莫不有 赐额大院。堂斋之敞。廪■(广畐)之厚。使令之备。足以养生徒数十人。终年而无匮乏之患。逐岁而有继给之资。其入享之贤。实一世之所共尊。后学之所模范。而往来便近。居处静閒。为士者孰不欲乐赴。而今反避之。惟恐不远。诚可惜也。其几只在长贰之得其人。诚自营门定为节目。申请 朝命。博询公议。择人而处之。略如宋时奉祠之例。以杜挟私轮差之弊。使任本院教导之责。每岁首。通本州及所属州县士子。简取其子弟之可教者。聚教于本院。春秋讲习。俱有常式。及岁末。始会都会所教之士于乐斋。方伯亲自考问。验其所学浅深。拔其优者。充于岁荐之窠。则非但养育之道渐入著实。书院既痼
生请修白云洞于丰基。致其眷眷。先后一揆者。何也。盖以校学有程式功令之拘。而书院宜宽閒讲习之方。是以书院之设最盛于南宋与我 朝之岭南。究厥本意。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道。岂少补哉。只缘世远教弛。风俗败坏。目今书院并土田。聚民丁于一处。大则为党论争夺之场。小则作閒谈讨食之所。掌教化者。亦宜夫留心度势。转移纠正。以不负昔贤之意也。凡小郡僻县建祠尸祝之所。置而不论。其大州府为都会三五处。莫不有 赐额大院。堂斋之敞。廪■(广畐)之厚。使令之备。足以养生徒数十人。终年而无匮乏之患。逐岁而有继给之资。其入享之贤。实一世之所共尊。后学之所模范。而往来便近。居处静閒。为士者孰不欲乐赴。而今反避之。惟恐不远。诚可惜也。其几只在长贰之得其人。诚自营门定为节目。申请 朝命。博询公议。择人而处之。略如宋时奉祠之例。以杜挟私轮差之弊。使任本院教导之责。每岁首。通本州及所属州县士子。简取其子弟之可教者。聚教于本院。春秋讲习。俱有常式。及岁末。始会都会所教之士于乐斋。方伯亲自考问。验其所学浅深。拔其优者。充于岁荐之窠。则非但养育之道渐入著实。书院既痼息山先生续集卷之四 第 1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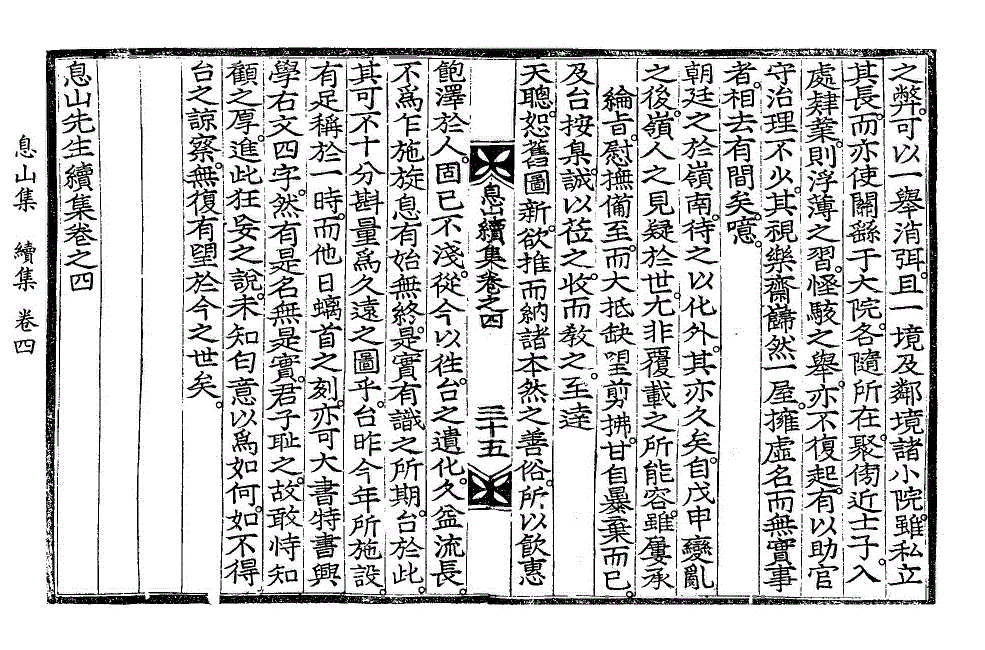 之弊。可以一举消弭。且一境及邻境诸小院。虽私立其长。而亦使关繇于大院。各随所在。聚傍近士子。入处肄业。则浮薄之习。怪骇之举。亦不复起。有以助官守治理不少。其视乐斋岿然一屋。拥虚名而无实事者。相去有间矣。噫。 朝廷之于岭南。待之以化外。其亦久矣。自戊申变乱之后。岭人之见疑于世。尤非覆载之所能容。虽屡承 纶旨。慰抚备至。而大抵缺望剪拂。甘自㬥弃而已。及台按臬。诚以莅之。收而教之。至达 天聪。恕旧图新。欲推而纳诸本然之善俗。所以饮惠饱泽于人。固已不浅。从今以往。台之遗化。久益流长。不为乍施旋息有始无终。是实有识之所期。台于此。其可不十分斟量为久远之图乎。台昨今年所施设。有足称于一时。而他日螭首之刻。亦可大书特书兴学右文四字。然有是名无是实。君子耻之。故敢恃知顾之厚。进此狂妄之说。未知匀意以为如何。如不得台之谅察。无复有望于今之世矣。
之弊。可以一举消弭。且一境及邻境诸小院。虽私立其长。而亦使关繇于大院。各随所在。聚傍近士子。入处肄业。则浮薄之习。怪骇之举。亦不复起。有以助官守治理不少。其视乐斋岿然一屋。拥虚名而无实事者。相去有间矣。噫。 朝廷之于岭南。待之以化外。其亦久矣。自戊申变乱之后。岭人之见疑于世。尤非覆载之所能容。虽屡承 纶旨。慰抚备至。而大抵缺望剪拂。甘自㬥弃而已。及台按臬。诚以莅之。收而教之。至达 天聪。恕旧图新。欲推而纳诸本然之善俗。所以饮惠饱泽于人。固已不浅。从今以往。台之遗化。久益流长。不为乍施旋息有始无终。是实有识之所期。台于此。其可不十分斟量为久远之图乎。台昨今年所施设。有足称于一时。而他日螭首之刻。亦可大书特书兴学右文四字。然有是名无是实。君子耻之。故敢恃知顾之厚。进此狂妄之说。未知匀意以为如何。如不得台之谅察。无复有望于今之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