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x 页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杂著
杂著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4H 页
 理气论
理气论太极生两仪。太极者理也。两仪者气也。两仪生而万物分焉。万物元来只是一太极而已。窃尝有疑于孟子中庸论理与气有所不同焉。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朱子释之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是乃兼人物而论之。以此推之。是人物之生。理同而气异也。孟子答告子之言曰。牛之性。犹人之性欤。朱子释之曰。以气而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以全哉。然则是人物之生。气同而理异也。盖大化流行。万物皆由是气而出焉。同禀此理。则人物所得之理气。何尝有异焉。然而中庸与孟子所论有人与物之不同。而不同之论。又不同焉。此不可以不辨者也。姑就平日所闻而认得者论之。以俟知者。盖尝论之。即乎万物有生之初。而以理言之。则浑然一理。流行不息。无始无终。随其气之成形而赋与之。夫理无有不善。亦无有不同。则人物之所禀。同一理也。何尝有人与物之分焉。此理之所以同也。以气而言之。则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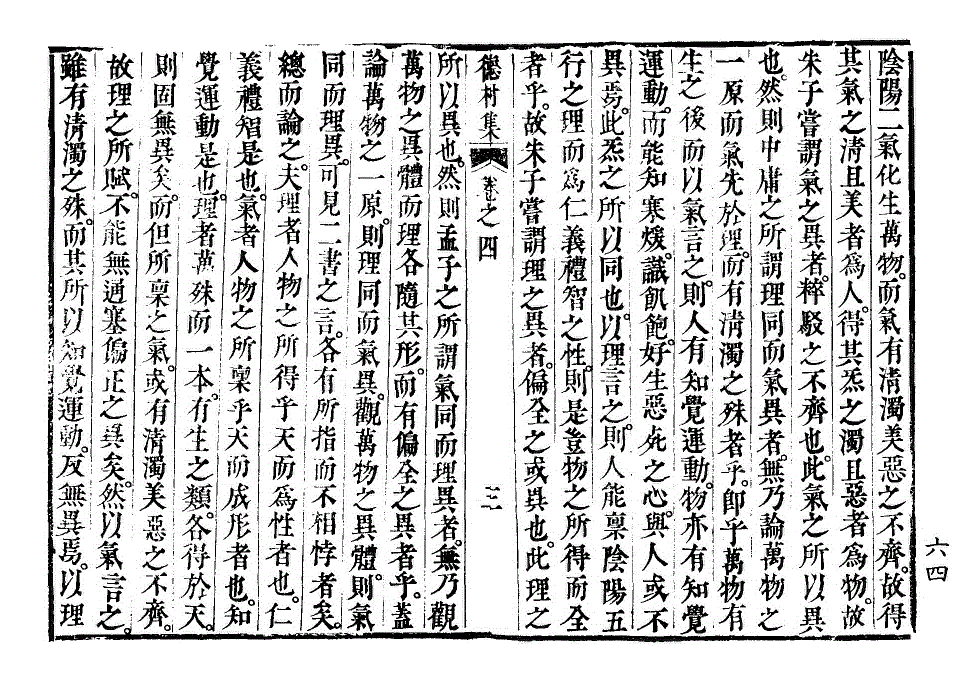 阴阳二气化生万物。而气有清浊美恶之不齐。故得其气之清且美者为人。得其气之浊且恶者为物。故朱子尝谓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也。此气之所以异也。然则中庸之所谓理同而气异者。无乃论万物之一原而气先于理。而有清浊之殊者乎。即乎万物有生之后而以气言之。则人有知觉运动。物亦有知觉运动。而能知寒煖。识饥饱。好生恶死之心。与人或不异焉。此气之所以同也。以理言之。则人能禀阴阳五行之理而为仁义礼智之性。则是岂物之所得而全者乎。故朱子尝谓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也。此理之所以异也。然则孟子之所谓气同而理异者。无乃观万物之异体而理各随其形。而有偏全之异者乎。盖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同而理异。可见二书之言。各有所指而不相悖者矣。总而论之。夫理者人物之所得乎天而为性者也。仁义礼智是也。气者人物之所禀乎天而成形者也。知觉运动是也。理者万殊而一本。有生之类。各得于天。则固无异矣。而但所禀之气。或有清浊美恶之不齐。故理之所赋。不能无通塞偏正之异矣。然以气言之。虽有清浊之殊。而其所以知觉运动。反无异焉。以理
阴阳二气化生万物。而气有清浊美恶之不齐。故得其气之清且美者为人。得其气之浊且恶者为物。故朱子尝谓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也。此气之所以异也。然则中庸之所谓理同而气异者。无乃论万物之一原而气先于理。而有清浊之殊者乎。即乎万物有生之后而以气言之。则人有知觉运动。物亦有知觉运动。而能知寒煖。识饥饱。好生恶死之心。与人或不异焉。此气之所以同也。以理言之。则人能禀阴阳五行之理而为仁义礼智之性。则是岂物之所得而全者乎。故朱子尝谓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也。此理之所以异也。然则孟子之所谓气同而理异者。无乃观万物之异体而理各随其形。而有偏全之异者乎。盖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同而理异。可见二书之言。各有所指而不相悖者矣。总而论之。夫理者人物之所得乎天而为性者也。仁义礼智是也。气者人物之所禀乎天而成形者也。知觉运动是也。理者万殊而一本。有生之类。各得于天。则固无异矣。而但所禀之气。或有清浊美恶之不齐。故理之所赋。不能无通塞偏正之异矣。然以气言之。虽有清浊之殊。而其所以知觉运动。反无异焉。以理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5H 页
 言之。其本虽同。而人之有五常之德而至虚至灵者。岂庶物之所可比哉。大抵论其理气之本源。则虽有理然后有气。若论其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而俱。是知气者载理之器也。故孔子曰。有物有则。其是之谓欤。是故人则得其气之全者。故其于理也。亦随而全。物则得其气之偏者。故其于理也。亦随而偏。气既全则理虽欲不全。得乎。气既偏则理虽欲不偏。得乎。理之所以异者。乃气之所以不同也。人物之所以不同者。非理之故也。气使之然也。气全而理亦全者人也。气偏而理亦偏者物也。以此论之。人与物。气亦异而理亦异也。且天籍阴阳五行之气。流行变化。以生万物。则是理不外乎气。气亦不外乎理。而人物同出乎天。则理亦天之理也。气亦天之气也。理虽有偏全之或异。气虽有清浊之不齐。其归皆本乎一原。则人与物。气亦同而理亦同也。其理气不测之妙用。可谓微矣。虽然。岂独人与物为然哉。人有圣与愚之不同。物亦有麟与枭之不类。此岂理之使然哉。气使之然也。盖人虽谓之得气之清者。至于愚则得气之浊者也。物虽谓之得气之浊者。至于麟则得气之清者也。故曰圣则人中之人。愚则人中之物。枭则物中之物。
言之。其本虽同。而人之有五常之德而至虚至灵者。岂庶物之所可比哉。大抵论其理气之本源。则虽有理然后有气。若论其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而俱。是知气者载理之器也。故孔子曰。有物有则。其是之谓欤。是故人则得其气之全者。故其于理也。亦随而全。物则得其气之偏者。故其于理也。亦随而偏。气既全则理虽欲不全。得乎。气既偏则理虽欲不偏。得乎。理之所以异者。乃气之所以不同也。人物之所以不同者。非理之故也。气使之然也。气全而理亦全者人也。气偏而理亦偏者物也。以此论之。人与物。气亦异而理亦异也。且天籍阴阳五行之气。流行变化。以生万物。则是理不外乎气。气亦不外乎理。而人物同出乎天。则理亦天之理也。气亦天之气也。理虽有偏全之或异。气虽有清浊之不齐。其归皆本乎一原。则人与物。气亦同而理亦同也。其理气不测之妙用。可谓微矣。虽然。岂独人与物为然哉。人有圣与愚之不同。物亦有麟与枭之不类。此岂理之使然哉。气使之然也。盖人虽谓之得气之清者。至于愚则得气之浊者也。物虽谓之得气之浊者。至于麟则得气之清者也。故曰圣则人中之人。愚则人中之物。枭则物中之物。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5L 页
 麟则物中之人也。呜呼。理气本原。物皆同得。而况于人乎。圣何人也。我何人也。气虽有不齐。理岂有不同。苟能矫揉乎气。省察乎理。以直养而无害。则浩然不馁。刚大之体。塞乎天地之间。仰不愧俯不怍矣。人中之物。吾知免夫。噫。悠悠天下。人何少而物何多也。理耶气耶。抑亦人耶。勖哉。吾党可不勉哉。非曰能知。愿学焉。
麟则物中之人也。呜呼。理气本原。物皆同得。而况于人乎。圣何人也。我何人也。气虽有不齐。理岂有不同。苟能矫揉乎气。省察乎理。以直养而无害。则浩然不馁。刚大之体。塞乎天地之间。仰不愧俯不怍矣。人中之物。吾知免夫。噫。悠悠天下。人何少而物何多也。理耶气耶。抑亦人耶。勖哉。吾党可不勉哉。非曰能知。愿学焉。观望月赋
维春孟之十五。云余坐乎中堂。客有来兮可人。聊与同而彷徨。纷相携而论道。深院静兮夜未央。黑云捲而天清。素月出而流光。圆光满而无缺。辉煌煌其照四方。客揖余而飏言。子亦知夫月之理乎。曾闻之夫古人。愿为子而言之。维厥精为太阴。本有质而无光。伊团团之一物。与银丸兮何异。然是气之所聚。体淡淡而空虚。故能受乎日光。致如彼之耀辉。若有时兮晦朔。乃承背之有异。盖夫天之周围。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丽而环绕。厥行用夫参差。日一周而为速。月十二而不及。十二积至三十。乃云协于厥数。是时即为晦日。爰与日而同度。月在下而背日。致下面之无光。自此以后渐远。及三日而明生。到十五而为望。日在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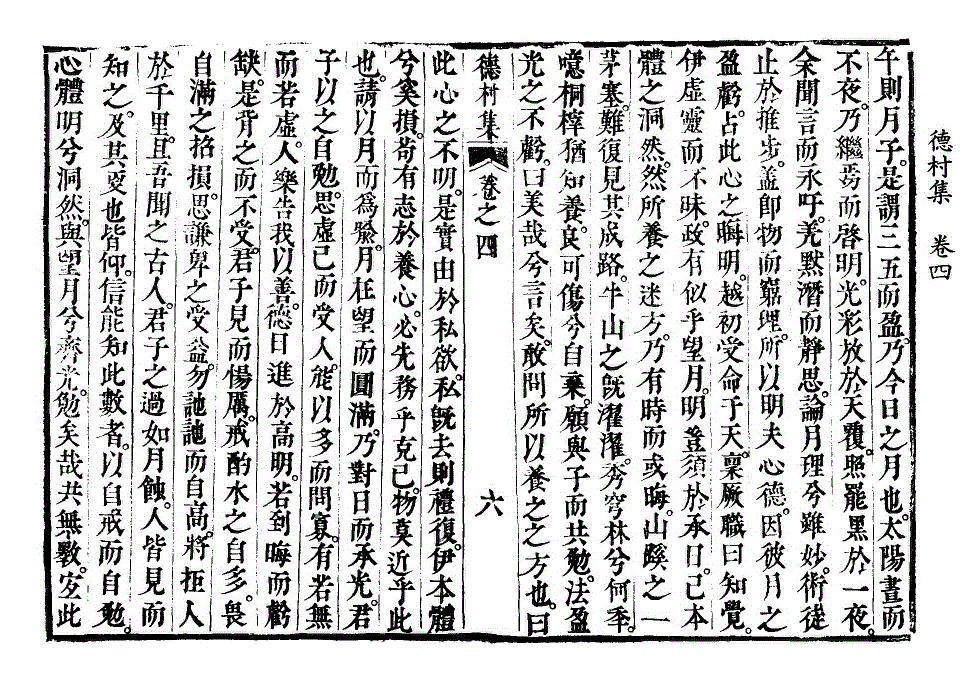 午则月子。是谓三五而盈。乃今日之月也。太阳昼而不夜。乃继焉而启明。光彩放于天覆。照罢黑于一夜。余闻言而永吁。羌默潜而静思。论月理兮虽妙。术徒止于推步。盖即物而穷理。所以明夫心德。因彼月之盈亏。占此心之晦明。越初受命于天。禀厥职曰知觉。伊虚灵而不昧。政有似乎望月。明岂须于承日。已本体之洞然。然所养之迷方。乃有时而或晦。山蹊之一茅塞。难复见其成路。牛山之既濯濯。秀穹林兮何年。噫桐梓犹知养。良可伤兮自弃。愿与子而共勉。法盈光之不亏。曰美哉兮言矣。敢问所以养之之方也。曰此心之不明。是实由于私欲。私既去则礼复。伊本体兮奚损。苟有志于养心。必先务乎克己。物莫近乎此也。请以月而为喻。月在望而圆满。乃对日而承光。君子以之自勉。思虚己而受人。能以多而问寡。有若无而若虚。人乐告我以善。德日进于高明。若到晦而亏缺。是背之而不受。君子见而惕厉。戒酌水之自多。畏自满之招损。思谦卑之受益。勿訑訑而自高。将拒人于千里。且吾闻之古人。君子之过如月蚀。人皆见而知之。及其更也皆仰。信能知此数者。以自戒而自勉。心体明兮洞然。与望月兮齐光。勉矣哉共无斁。宜此
午则月子。是谓三五而盈。乃今日之月也。太阳昼而不夜。乃继焉而启明。光彩放于天覆。照罢黑于一夜。余闻言而永吁。羌默潜而静思。论月理兮虽妙。术徒止于推步。盖即物而穷理。所以明夫心德。因彼月之盈亏。占此心之晦明。越初受命于天。禀厥职曰知觉。伊虚灵而不昧。政有似乎望月。明岂须于承日。已本体之洞然。然所养之迷方。乃有时而或晦。山蹊之一茅塞。难复见其成路。牛山之既濯濯。秀穹林兮何年。噫桐梓犹知养。良可伤兮自弃。愿与子而共勉。法盈光之不亏。曰美哉兮言矣。敢问所以养之之方也。曰此心之不明。是实由于私欲。私既去则礼复。伊本体兮奚损。苟有志于养心。必先务乎克己。物莫近乎此也。请以月而为喻。月在望而圆满。乃对日而承光。君子以之自勉。思虚己而受人。能以多而问寡。有若无而若虚。人乐告我以善。德日进于高明。若到晦而亏缺。是背之而不受。君子见而惕厉。戒酌水之自多。畏自满之招损。思谦卑之受益。勿訑訑而自高。将拒人于千里。且吾闻之古人。君子之过如月蚀。人皆见而知之。及其更也皆仰。信能知此数者。以自戒而自勉。心体明兮洞然。与望月兮齐光。勉矣哉共无斁。宜此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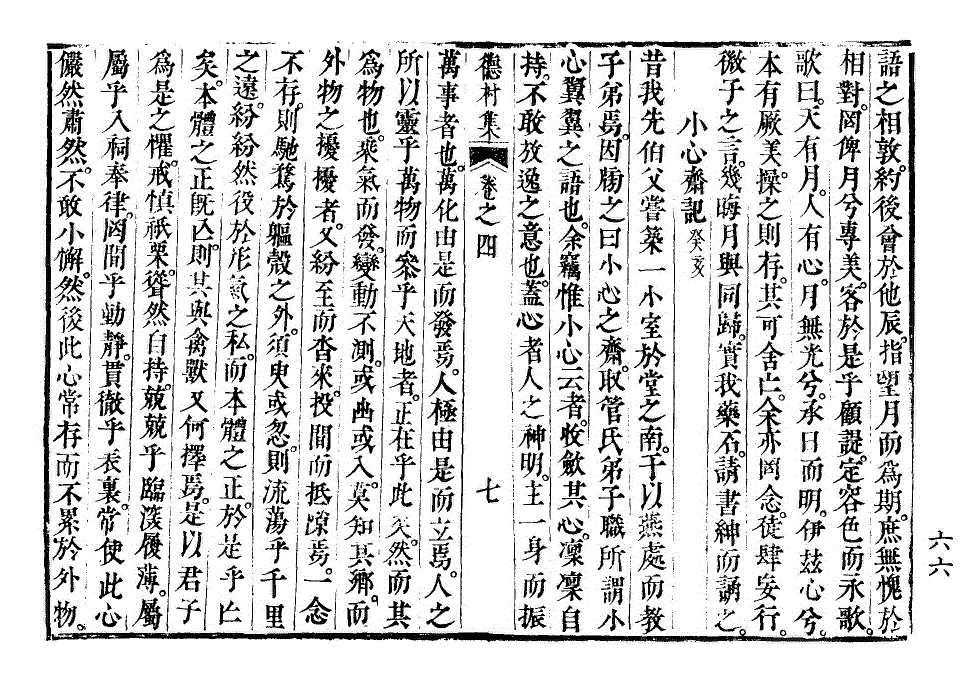 语之相敦。约后会于他辰。指望月而为期。庶无愧于相对。罔俾月兮专美。客于是乎顾諟。定容色而永歌。歌曰。天有月。人有心。月无光兮。承日而明。伊玆心兮。本有厥美。操之则存。其可舍亡。余亦罔念。徒肆妄行。微子之言。几晦月与同归。实我药石。请书绅而诵之。
语之相敦。约后会于他辰。指望月而为期。庶无愧于相对。罔俾月兮专美。客于是乎顾諟。定容色而永歌。歌曰。天有月。人有心。月无光兮。承日而明。伊玆心兮。本有厥美。操之则存。其可舍亡。余亦罔念。徒肆妄行。微子之言。几晦月与同归。实我药石。请书绅而诵之。小心斋记(癸亥)
昔我先伯父尝筑一小室于堂之南。于以燕处而教子弟焉。因榜之曰小心之斋。取管氏弟子职所谓小心翼翼之语也。余窃惟小心云者。收敛其心。凛凛自持。不敢放逸之意也。盖心者人之神明。主一身而振万事者也。万化由是而发焉。人极由是而立焉。人之所以灵乎万物而参乎天地者。正在乎此矣。然而其为物也。乘气而发。变动不测。或出或入。莫知其乡。而外物之扰扰者。又纷至而沓来。投间而抵隙焉。一念不存。则驰骛于躯壳之外。须臾或忽。则流荡乎千里之远。纷纷然役于形气之私。而本体之正。于是乎亡矣。本体之正既亡。则其与禽兽又何择焉。是以君子为是之惧。戒慎祇栗。耸然自持。兢兢乎临深履薄。属属乎入祠奉律。罔间乎动静。贯彻乎表里。常使此心俨然肃然。不敢小懈。然后此心常存而不累于外物。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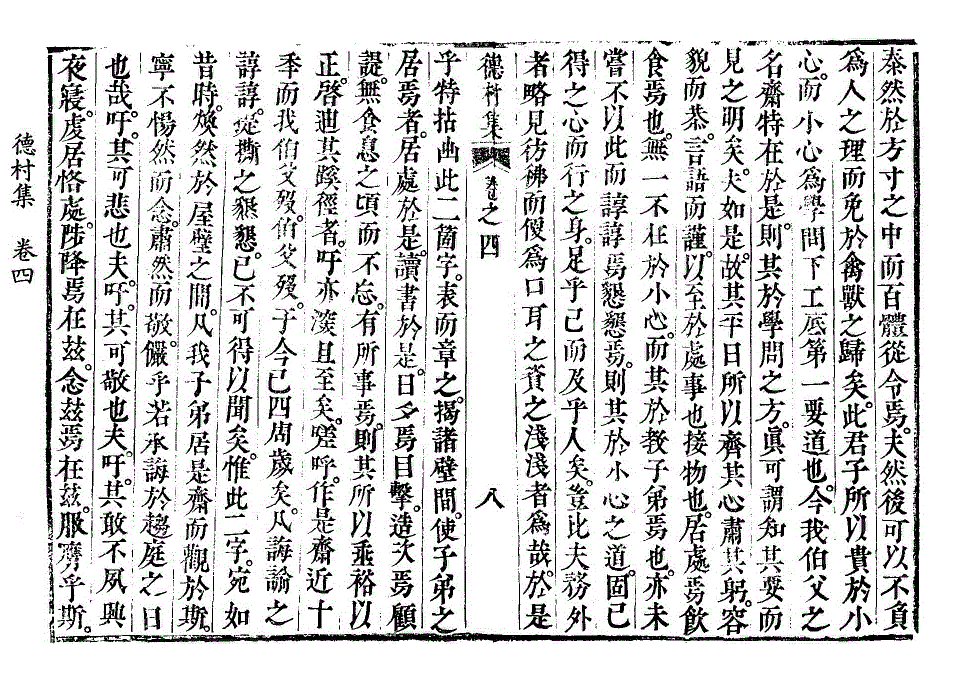 泰然于方寸之中而百体从令焉。夫然后可以不负为人之理而免于禽兽之归矣。此君子所以贵于小心。而小心为学问下工底第一要道也。今我伯父之名斋特在于是。则其于学问之方。真可谓知其要而见之明矣。夫如是。故其平日所以齐其心肃其躬。容貌而恭。言语而谨。以至于处事也接物也。居处焉饮食焉也。无一不在于小心。而其于教子弟焉也。亦未尝不以此而谆谆焉恳恳焉。则其于小心之道。固已得之心而行之身。足乎己而及乎人矣。岂比夫务外者略见彷佛而便为口耳之资之浅浅者为哉。于是乎特拈出此二个字。表而章之。揭诸壁间。使子弟之居焉者。居处于是。读书于是。日夕焉目击。造次焉顾諟。无食息之顷而不忘。有所事焉。则其所以垂裕以正。启迪其蹊径者。吁亦深且至矣。嗟呼。作是斋近十年而我伯父殁。伯父殁。于今已四周岁矣。凡诲谕之谆谆。提撕之恳恳。已不可得以闻矣。惟此二字。宛如昔时。焕然于屋壁之间。凡我子弟居是斋而观于斯。宁不惕然而念。肃然而敬。俨乎若承诲于趋庭之日也哉。吁。其可悲也夫。吁。其可敬也夫。吁。其敢不夙兴夜寝。虔居恪处。陟降焉在玆。念玆焉在玆。服膺乎斯。
泰然于方寸之中而百体从令焉。夫然后可以不负为人之理而免于禽兽之归矣。此君子所以贵于小心。而小心为学问下工底第一要道也。今我伯父之名斋特在于是。则其于学问之方。真可谓知其要而见之明矣。夫如是。故其平日所以齐其心肃其躬。容貌而恭。言语而谨。以至于处事也接物也。居处焉饮食焉也。无一不在于小心。而其于教子弟焉也。亦未尝不以此而谆谆焉恳恳焉。则其于小心之道。固已得之心而行之身。足乎己而及乎人矣。岂比夫务外者略见彷佛而便为口耳之资之浅浅者为哉。于是乎特拈出此二个字。表而章之。揭诸壁间。使子弟之居焉者。居处于是。读书于是。日夕焉目击。造次焉顾諟。无食息之顷而不忘。有所事焉。则其所以垂裕以正。启迪其蹊径者。吁亦深且至矣。嗟呼。作是斋近十年而我伯父殁。伯父殁。于今已四周岁矣。凡诲谕之谆谆。提撕之恳恳。已不可得以闻矣。惟此二字。宛如昔时。焕然于屋壁之间。凡我子弟居是斋而观于斯。宁不惕然而念。肃然而敬。俨乎若承诲于趋庭之日也哉。吁。其可悲也夫。吁。其可敬也夫。吁。其敢不夙兴夜寝。虔居恪处。陟降焉在玆。念玆焉在玆。服膺乎斯。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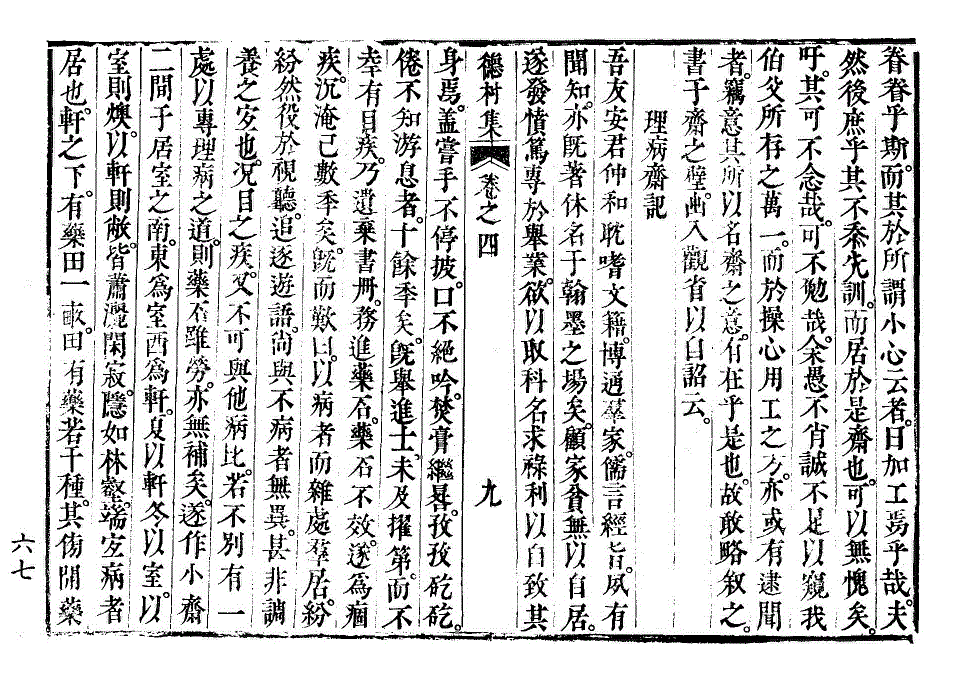 眷眷乎斯。而其于所谓小心云者。日加工焉乎哉。夫然后庶乎其不忝先训。而居于是斋也。可以无愧矣。吁。其可不念哉。可不勉哉。余愚不肖诚不足以窥我伯父所存之万一。而于操心用工之方。亦或有逮闻者。窃意其所以名斋之意。有在乎是也。故敢略叙之。书于斋之壁。出入观省以自诏云。
眷眷乎斯。而其于所谓小心云者。日加工焉乎哉。夫然后庶乎其不忝先训。而居于是斋也。可以无愧矣。吁。其可不念哉。可不勉哉。余愚不肖诚不足以窥我伯父所存之万一。而于操心用工之方。亦或有逮闻者。窃意其所以名斋之意。有在乎是也。故敢略叙之。书于斋之壁。出入观省以自诏云。理病斋记
吾友安君仲和耽嗜文籍。博通群家。儒言经旨。夙有闻知。亦既著休名于翰墨之场矣。顾家贫无以自居。遂发愤笃专于举业。欲以取科名求禄利以自致其身焉。盖尝手不停披。口不绝吟。焚膏继晷。孜孜矻矻。倦不知游息者。十馀年矣。既举进士。未及擢第。而不幸有目疾。乃遗弃书册。务进药石。药石不效。遂为痼疾。沉淹已数年矣。既而叹曰。以病者而杂处群居。纷纷然役于视听。追逐游语。尚与不病者无异。甚非调养之宜也。况目之疾。又不可与他病比。若不别有一处以专理病之道。则药石虽劳。亦无补矣。遂作小斋二间于居室之南。东为室西为轩。夏以轩冬以室。以室则燠。以轩则敝。皆萧洒闲寂。隐如林壑。端宜病者居也。轩之下。有药田一亩。田有药若干种。其傍开药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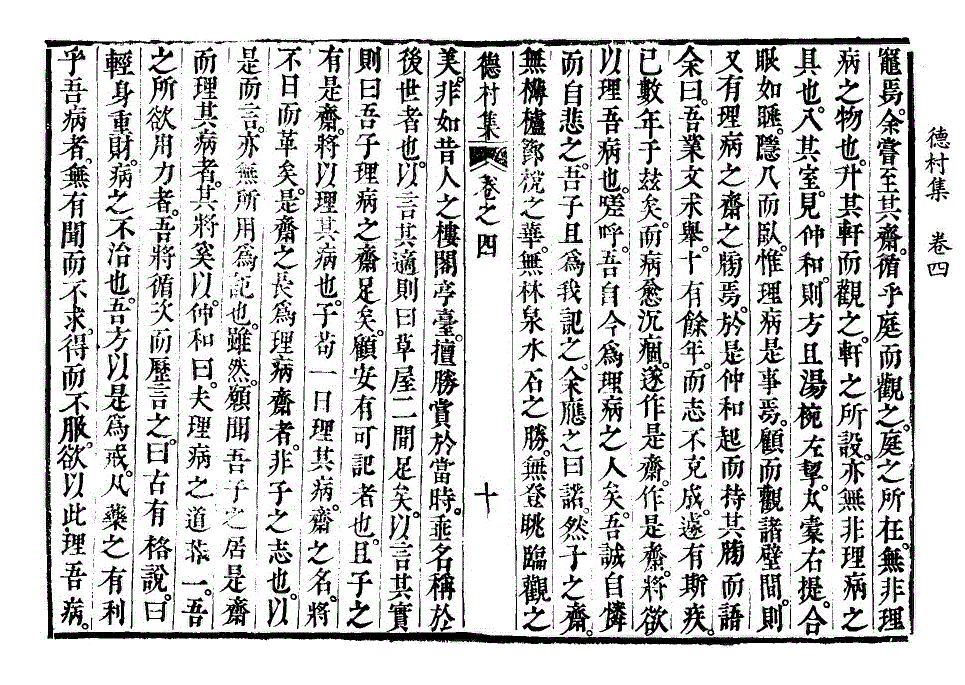 灶焉。余尝至其斋。循乎庭而观之。庭之所在。无非理病之物也。升其轩而观之。轩之所设。亦无非理病之具也。入其室。见仲和。则方且汤碗左挈。丸橐右提。合眼如睡。隐几而卧。惟理病是事焉。顾而观诸壁间。则又有理病之斋之榜焉。于是仲和起而持其榜而语余曰。吾业文求举。十有馀年。而志不克成。遽有斯疾。已数年于玆矣。而病愈沉痼。遂作是斋。作是斋。将欲以理吾病也。嗟呼。吾自今为理病之人矣。吾诚自怜而自悲之。吾子且为我记之。余应之曰诺。然子之斋。无欂栌节棁之华。无林泉水石之胜。无登眺临观之美。非如昔人之楼阁亭台。擅胜赏于当时。垂名称于后世者也。以言其适则曰草屋二间足矣。以言其实则曰吾子理病之斋足矣。顾安有可记者也。且子之有是斋。将以理其病也。子苟一日理其病。斋之名。将不日而革矣。是斋之长为理病斋者。非子之志也。以是而言。亦无所用为记也。虽然。愿闻吾子之居是斋而理其病者。其将奚以。仲和曰。夫理病之道非一。吾之所欲用力者。吾将循次而历言之。曰古有格说。曰轻身重财。病之不治也。吾方以是为戒。凡药之有利乎吾病者。无有闻而不求。得而不服。欲以此理吾病。
灶焉。余尝至其斋。循乎庭而观之。庭之所在。无非理病之物也。升其轩而观之。轩之所设。亦无非理病之具也。入其室。见仲和。则方且汤碗左挈。丸橐右提。合眼如睡。隐几而卧。惟理病是事焉。顾而观诸壁间。则又有理病之斋之榜焉。于是仲和起而持其榜而语余曰。吾业文求举。十有馀年。而志不克成。遽有斯疾。已数年于玆矣。而病愈沉痼。遂作是斋。作是斋。将欲以理吾病也。嗟呼。吾自今为理病之人矣。吾诚自怜而自悲之。吾子且为我记之。余应之曰诺。然子之斋。无欂栌节棁之华。无林泉水石之胜。无登眺临观之美。非如昔人之楼阁亭台。擅胜赏于当时。垂名称于后世者也。以言其适则曰草屋二间足矣。以言其实则曰吾子理病之斋足矣。顾安有可记者也。且子之有是斋。将以理其病也。子苟一日理其病。斋之名。将不日而革矣。是斋之长为理病斋者。非子之志也。以是而言。亦无所用为记也。虽然。愿闻吾子之居是斋而理其病者。其将奚以。仲和曰。夫理病之道非一。吾之所欲用力者。吾将循次而历言之。曰古有格说。曰轻身重财。病之不治也。吾方以是为戒。凡药之有利乎吾病者。无有闻而不求。得而不服。欲以此理吾病。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8L 页
 余曰。善则善矣。犹未可以理也。仲和曰。古有明目之方六。曰损读书减思虑。专内视简外观。朝晚起夜早眠是已。吾方从事斯六者。欲以此理吾病。余曰。善则善矣。犹未可以理也。仲和曰。昔人有言近女室。疾如蛊惑以丧志。淫生六疾。吾方深戒于玆。惟远房室是务。欲以此理吾病。余曰。善则善矣。犹未可以理也。仲和曰。昔人有言心动万病生。心静万病息。吾方服膺乎玆。惟静心是务。欲以此理吾病。余曰。至矣善矣。蔑以加矣。虽然。抑又有一说焉。夫心不可强使之静也。惟明于得丧悲欢之域者几矣。夫得丧一理。悲欢一涂。其来也。不可以却。其去也。不可以止。夫奚避奚处。奚就奚去。明乎是者。是谓无累。无累则心静。心静则形不劳。形不劳则精不亏。目者精之会也。形之粹也。形全精复。目乃明矣。曩子之未有斯疾也。役役焉惟科名是求。此以得丧累其心也。得丧为之累。故心不静。心不静故形劳。形劳故精亏。无惑乎子之有斯疾也。今也。又戚戚焉惟其疾是悲。此以悲欢累其心也。悲欢为之累。心安得静。形安得不劳。精安得不亏哉。亦无惑乎子之抱疾数年而犹未能理也。是故得丧悲欢为之累。则心虽欲强使之静。亦不可得也。心既
余曰。善则善矣。犹未可以理也。仲和曰。古有明目之方六。曰损读书减思虑。专内视简外观。朝晚起夜早眠是已。吾方从事斯六者。欲以此理吾病。余曰。善则善矣。犹未可以理也。仲和曰。昔人有言近女室。疾如蛊惑以丧志。淫生六疾。吾方深戒于玆。惟远房室是务。欲以此理吾病。余曰。善则善矣。犹未可以理也。仲和曰。昔人有言心动万病生。心静万病息。吾方服膺乎玆。惟静心是务。欲以此理吾病。余曰。至矣善矣。蔑以加矣。虽然。抑又有一说焉。夫心不可强使之静也。惟明于得丧悲欢之域者几矣。夫得丧一理。悲欢一涂。其来也。不可以却。其去也。不可以止。夫奚避奚处。奚就奚去。明乎是者。是谓无累。无累则心静。心静则形不劳。形不劳则精不亏。目者精之会也。形之粹也。形全精复。目乃明矣。曩子之未有斯疾也。役役焉惟科名是求。此以得丧累其心也。得丧为之累。故心不静。心不静故形劳。形劳故精亏。无惑乎子之有斯疾也。今也。又戚戚焉惟其疾是悲。此以悲欢累其心也。悲欢为之累。心安得静。形安得不劳。精安得不亏哉。亦无惑乎子之抱疾数年而犹未能理也。是故得丧悲欢为之累。则心虽欲强使之静。亦不可得也。心既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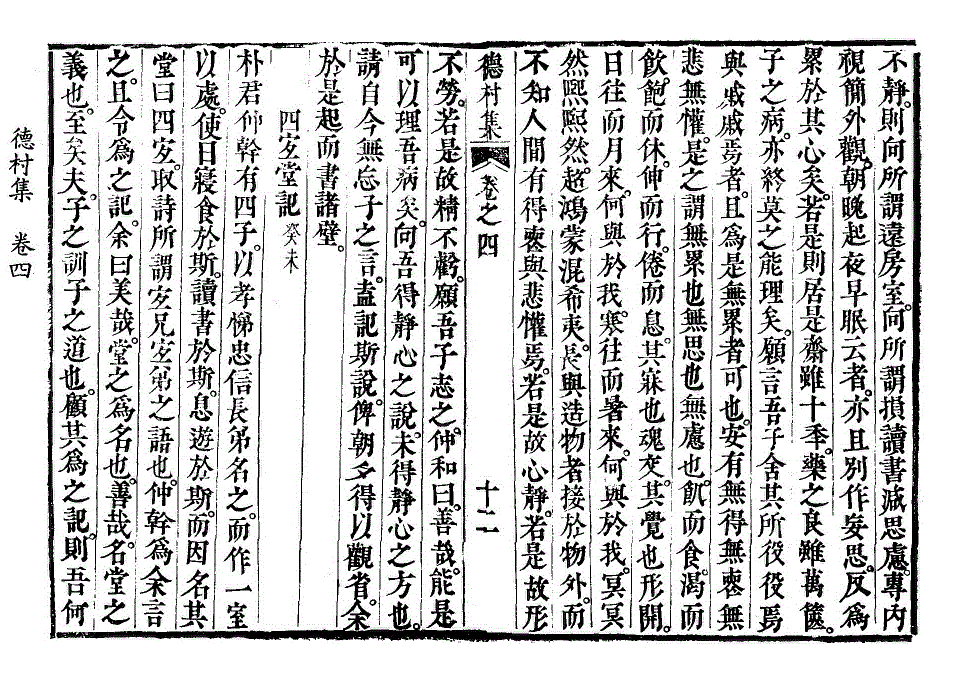 不静。则向所谓远房室。向所谓损读书减思虑。专内视简外观。朝晚起夜早眠云者。亦且别作妄思。反为累于其心矣。若是则居是斋虽十年。药之良虽万箧。子之病。亦终莫之能理矣。愿言吾子舍其所役役焉与戚戚焉者。且为是无累者可也。安有无得无丧无悲无欢。是之谓无累也无思也无虑也。饥而食。渴而饮。饱而休。伸而行。倦而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日往而月来。何与于我。寒往而暑来。何与于我。冥冥然熙熙然。超鸿蒙混希夷。长与造物者接于物外。而不知人间有得丧与悲欢焉。若是故心静。若是故形不劳。若是故精不亏。愿吾子志之。仲和曰。善哉。能是可以理吾病矣。向吾得静心之说。未得静心之方也。请自今无忘子之言。盍记斯说。俾朝夕得以观省。余于是起而书诸壁。
不静。则向所谓远房室。向所谓损读书减思虑。专内视简外观。朝晚起夜早眠云者。亦且别作妄思。反为累于其心矣。若是则居是斋虽十年。药之良虽万箧。子之病。亦终莫之能理矣。愿言吾子舍其所役役焉与戚戚焉者。且为是无累者可也。安有无得无丧无悲无欢。是之谓无累也无思也无虑也。饥而食。渴而饮。饱而休。伸而行。倦而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日往而月来。何与于我。寒往而暑来。何与于我。冥冥然熙熙然。超鸿蒙混希夷。长与造物者接于物外。而不知人间有得丧与悲欢焉。若是故心静。若是故形不劳。若是故精不亏。愿吾子志之。仲和曰。善哉。能是可以理吾病矣。向吾得静心之说。未得静心之方也。请自今无忘子之言。盍记斯说。俾朝夕得以观省。余于是起而书诸壁。四宜堂记(癸未)
朴君仲干有四子。以孝悌忠信长弟名之。而作一室以处。使日寝食于斯。读书于斯。息游于斯。而因名其堂曰四宜。取诗所谓宜兄宜弟之语也。仲干为余言之。且令为之记。余曰美哉。堂之为名也。善哉。名堂之义也。至矣夫。子之训子之道也。顾其为之记。则吾何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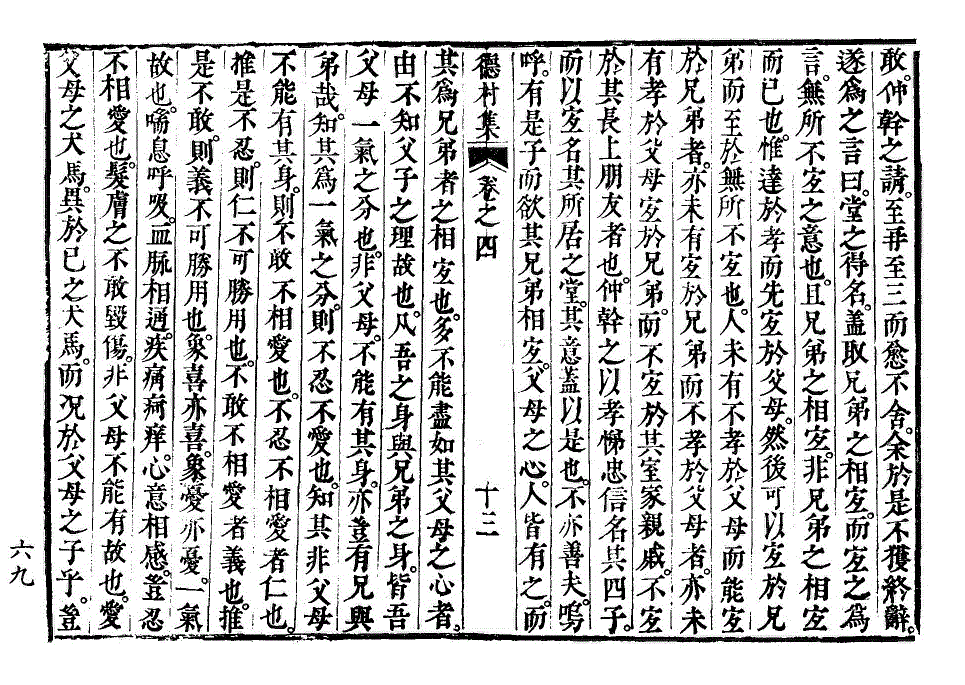 敢。仲干之请。至再至三而愈不舍。余于是不获终辞。遂为之言曰。堂之得名。盖取兄弟之相宜。而宜之为言。无所不宜之意也。且兄弟之相宜。非兄弟之相宜而已也。惟达于孝而先宜于父母。然后可以宜于兄弟而至于无所不宜也。人未有不孝于父母而能宜于兄弟者。亦未有宜于兄弟而不孝于父母者。亦未有孝于父母宜于兄弟。而不宜于其室家亲戚。不宜于其长上朋友者也。仲干之以孝悌忠信名其四子。而以宜名其所居之堂。其意盖以是也。不亦善夫。呜呼。有是子而欲其兄弟相宜。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其为兄弟者之相宜也。多不能尽如其父母之心者。由不知父子之理故也。凡吾之身与兄弟之身。皆吾父母一气之分也。非父母。不能有其身。亦岂有兄与弟哉。知其为一气之分。则不忍不爱也。知其非父母不能有其身。则不敢不相爱也。不忍不相爱者仁也。推是不忍。则仁不可胜用也。不敢不相爱者义也。推是不敢。则义不可胜用也。象喜亦喜。象忧亦忧。一气故也。喘息呼吸。血脉相通。疾痛疴痒。心意相感。岂忍不相爱也。发肤之不敢毁伤。非父母不能有故也。爱父母之犬马。异于己之犬马。而况于父母之子乎。岂
敢。仲干之请。至再至三而愈不舍。余于是不获终辞。遂为之言曰。堂之得名。盖取兄弟之相宜。而宜之为言。无所不宜之意也。且兄弟之相宜。非兄弟之相宜而已也。惟达于孝而先宜于父母。然后可以宜于兄弟而至于无所不宜也。人未有不孝于父母而能宜于兄弟者。亦未有宜于兄弟而不孝于父母者。亦未有孝于父母宜于兄弟。而不宜于其室家亲戚。不宜于其长上朋友者也。仲干之以孝悌忠信名其四子。而以宜名其所居之堂。其意盖以是也。不亦善夫。呜呼。有是子而欲其兄弟相宜。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其为兄弟者之相宜也。多不能尽如其父母之心者。由不知父子之理故也。凡吾之身与兄弟之身。皆吾父母一气之分也。非父母。不能有其身。亦岂有兄与弟哉。知其为一气之分。则不忍不爱也。知其非父母不能有其身。则不敢不相爱也。不忍不相爱者仁也。推是不忍。则仁不可胜用也。不敢不相爱者义也。推是不敢。则义不可胜用也。象喜亦喜。象忧亦忧。一气故也。喘息呼吸。血脉相通。疾痛疴痒。心意相感。岂忍不相爱也。发肤之不敢毁伤。非父母不能有故也。爱父母之犬马。异于己之犬马。而况于父母之子乎。岂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0H 页
 敢不相爱也。人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吾宗子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虽其等杀有分。循序有渐。今日之宜。未便至此。而元来宜字占地步。已到此界头。故其功效自有住不得者。盖自一源中流出。而莫非吾分内事也。仁义之兼众善而宜之为无所不宜者。乃如是也。仲干曰。噫。是可以训吾子矣。余曰。常棣之诗曰。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孥。而夫子称之曰。父母其顺矣乎。仲干以是训其子。而其子之相宜如此。则仲干之心。不既顺矣乎。仲干之心。既顺矣。而仲干之兄弟之相宜又如此。则上而至于尊君之心。亦不其顺矣乎。是可以记斯堂也。遂为之记。
敢不相爱也。人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吾宗子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虽其等杀有分。循序有渐。今日之宜。未便至此。而元来宜字占地步。已到此界头。故其功效自有住不得者。盖自一源中流出。而莫非吾分内事也。仁义之兼众善而宜之为无所不宜者。乃如是也。仲干曰。噫。是可以训吾子矣。余曰。常棣之诗曰。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孥。而夫子称之曰。父母其顺矣乎。仲干以是训其子。而其子之相宜如此。则仲干之心。不既顺矣乎。仲干之心。既顺矣。而仲干之兄弟之相宜又如此。则上而至于尊君之心。亦不其顺矣乎。是可以记斯堂也。遂为之记。曹汝中(锡厚)字说(辛未)
曹君既冠。以其名锡厚。请字于余。余辞以不敢。曹君曰。西湖朴丈尝命我曰汝中。是何如。余曰。甚当。曹君曰。盍为我略述其意以相勉焉。余亦以不敢为辞。而其请愈勤。且有说。不可得以终辞也。遂拜手而为之言曰。呜呼。天之于人。其锡之者。不亦厚哉。天之为天。其道不过曰元亨利贞。而天全以是锡之于人。曰仁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0L 页
 义礼智之性。其本也真而静。其德也神而广。寂然藏于方寸之中而众理毕具。感而通乎天下之故而万事悉举。其功也至于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以藐然一身。仰参三才。而天地与万物。亦必待是而位且育焉。斯子思所谓天命者。而诗所谓懿德也。呜呼。天之于人。其不亦锡之厚哉。此尊君所以命子之名也。然而拘之前。有气质之偏。蔽之后。有物欲之私。故欲动情胜而不知所以裁之。则其发之于外者。于是乎有过与不及而失厥中焉。既失厥中。何所不至。过者愈过。不及者愈不及。而去厥初日远矣。斯圣人之设教。学者之自治。必以中为标准。若射者之志于的。行者之归于家也。虽然。中也岂圣人所强说者哉。成汤曰。皇天降衷于下民。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盖天地之理。有自然之中。而人也得之以生。故其体浑然在中。其用蔼然见于日用彝伦之间。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惟在精择而固守。不为物欲所乱焉而已尔。不睹不闻。而亦不敢忽。俨然肃然。常若有临。存此中于未发之时也。一念之萌。而必察其几。或遏或存。欲理之分。审其中于已发之际也。存之于未发而无所偏倚则中之体立矣。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审之于已
义礼智之性。其本也真而静。其德也神而广。寂然藏于方寸之中而众理毕具。感而通乎天下之故而万事悉举。其功也至于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以藐然一身。仰参三才。而天地与万物。亦必待是而位且育焉。斯子思所谓天命者。而诗所谓懿德也。呜呼。天之于人。其不亦锡之厚哉。此尊君所以命子之名也。然而拘之前。有气质之偏。蔽之后。有物欲之私。故欲动情胜而不知所以裁之。则其发之于外者。于是乎有过与不及而失厥中焉。既失厥中。何所不至。过者愈过。不及者愈不及。而去厥初日远矣。斯圣人之设教。学者之自治。必以中为标准。若射者之志于的。行者之归于家也。虽然。中也岂圣人所强说者哉。成汤曰。皇天降衷于下民。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盖天地之理。有自然之中。而人也得之以生。故其体浑然在中。其用蔼然见于日用彝伦之间。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惟在精择而固守。不为物欲所乱焉而已尔。不睹不闻。而亦不敢忽。俨然肃然。常若有临。存此中于未发之时也。一念之萌。而必察其几。或遏或存。欲理之分。审其中于已发之际也。存之于未发而无所偏倚则中之体立矣。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审之于已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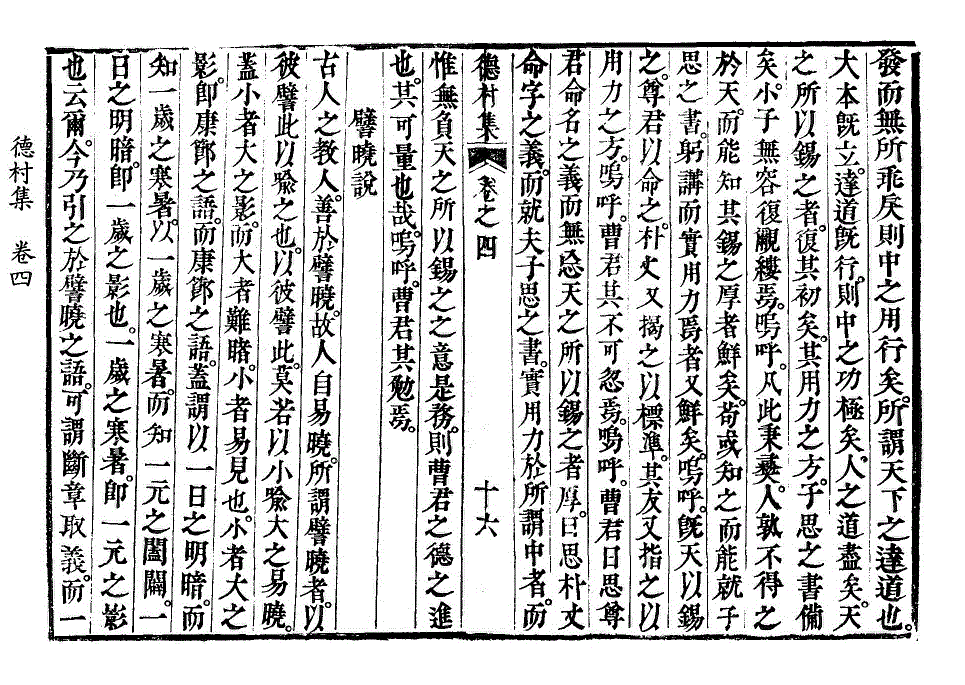 发而无所乖戾则中之用行矣。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大本既立。达道既行。则中之功极矣。人之道尽矣。天之所以锡之者。复其初矣。其用力之方。子思之书备矣。小子无容复覼缕焉。呜呼。凡此秉彝。人孰不得之于天。而能知其锡之厚者鲜矣。苟或知之而能就子思之书。躬讲而实用力焉者又鲜矣。呜呼。既天以锡之。尊君以命之。朴丈又揭之以标准。其友又指之以用力之方。呜呼。曹君其不可忽焉。呜呼。曹君日思尊君命名之义而无忘天之所以锡之者厚。日思朴丈命字之义。而就夫子思之书。实用力于所谓中者。而惟无负天之所以锡之之意是务。则曹君之德之进也。其可量也哉。呜呼。曹君其勉焉。
发而无所乖戾则中之用行矣。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大本既立。达道既行。则中之功极矣。人之道尽矣。天之所以锡之者。复其初矣。其用力之方。子思之书备矣。小子无容复覼缕焉。呜呼。凡此秉彝。人孰不得之于天。而能知其锡之厚者鲜矣。苟或知之而能就子思之书。躬讲而实用力焉者又鲜矣。呜呼。既天以锡之。尊君以命之。朴丈又揭之以标准。其友又指之以用力之方。呜呼。曹君其不可忽焉。呜呼。曹君日思尊君命名之义而无忘天之所以锡之者厚。日思朴丈命字之义。而就夫子思之书。实用力于所谓中者。而惟无负天之所以锡之之意是务。则曹君之德之进也。其可量也哉。呜呼。曹君其勉焉。譬晓说
古人之教人。善于譬晓。故人自易晓。所谓譬晓者。以彼譬此以喻之也。以彼譬此。莫若以小喻大之易晓。盖小者大之影。而大者难睹。小者易见也。小者大之影。即康节之语。而康节之语。盖谓以一日之明暗。而知一岁之寒暑。以一岁之寒暑。而知一元之阖辟。一日之明暗。即一岁之影也。一岁之寒暑。即一元之影也云尔。今乃引之于譬晓之语。可谓断章取义。而一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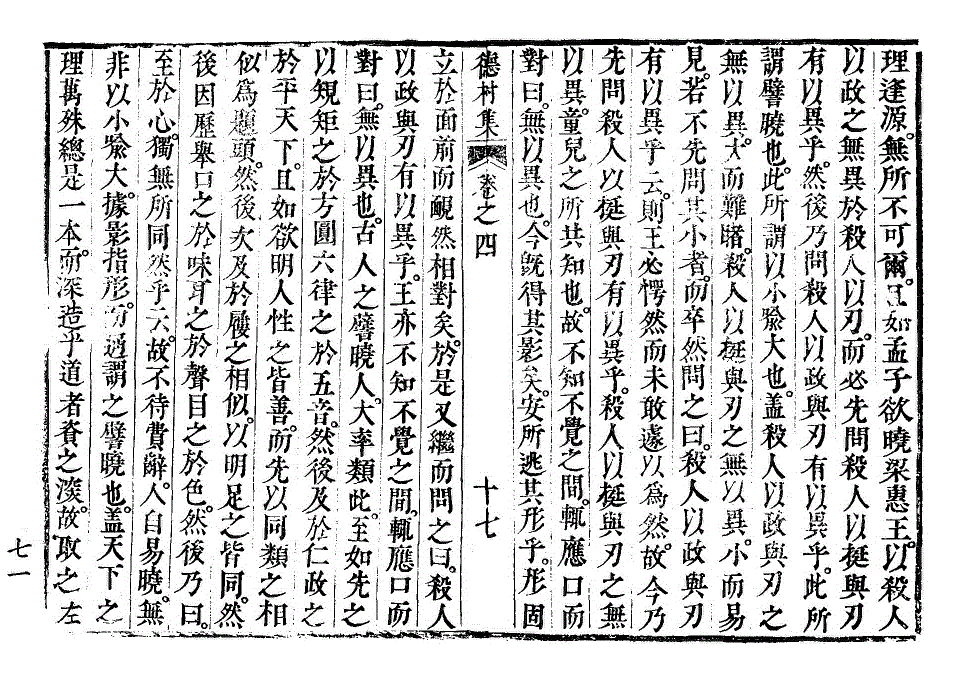 理逢源。无所不可尔。且如孟子欲晓梁惠王。以杀人以政之无异于杀人以刃。而必先问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然后乃问杀人以政与刃有以异乎。此所谓譬晓也。此所谓以小喻大也。盖杀人以政与刃之无以异。大而难睹。杀人以挺与刃之无以异。小而易见。若不先问其小者。而卒然问之曰。杀人以政与刃有以异乎云。则王必愕然而未敢遽以为然。故今乃先问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杀人以挺与刃之无以异。童儿之所共知也。故不知不觉之间。辄应口而对曰。无以异也。今既得其影矣。安所逃其形乎。形固立于面前而腼然相对矣。于是又继而问之曰。杀人以政与刃有以异乎。王亦不知不觉之间。辄应口而对曰。无以异也。古人之譬晓人。大率类此。至如先之以规矩之于方圆六律之于五音。然后及于仁政之于平天下。且如欲明人性之皆善。而先以同类之相似为题头。然后次及于屦之相似。以明足之皆同。然后因历举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然后乃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云。故不待费辞。人自易晓。无非以小喻大。据影指形。而通谓之譬晓也。盖天下之理万殊总是一本。而深造乎道者资之深。故取之左
理逢源。无所不可尔。且如孟子欲晓梁惠王。以杀人以政之无异于杀人以刃。而必先问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然后乃问杀人以政与刃有以异乎。此所谓譬晓也。此所谓以小喻大也。盖杀人以政与刃之无以异。大而难睹。杀人以挺与刃之无以异。小而易见。若不先问其小者。而卒然问之曰。杀人以政与刃有以异乎云。则王必愕然而未敢遽以为然。故今乃先问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杀人以挺与刃之无以异。童儿之所共知也。故不知不觉之间。辄应口而对曰。无以异也。今既得其影矣。安所逃其形乎。形固立于面前而腼然相对矣。于是又继而问之曰。杀人以政与刃有以异乎。王亦不知不觉之间。辄应口而对曰。无以异也。古人之譬晓人。大率类此。至如先之以规矩之于方圆六律之于五音。然后及于仁政之于平天下。且如欲明人性之皆善。而先以同类之相似为题头。然后次及于屦之相似。以明足之皆同。然后因历举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然后乃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云。故不待费辞。人自易晓。无非以小喻大。据影指形。而通谓之譬晓也。盖天下之理万殊总是一本。而深造乎道者资之深。故取之左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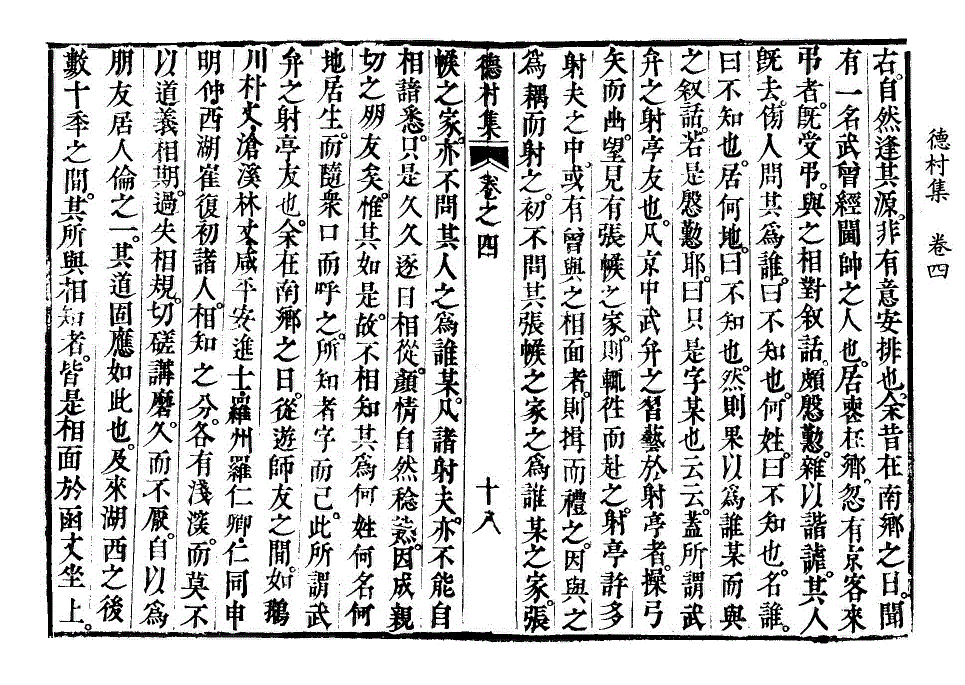 右。自然逢其源。非有意安排也。余昔在南乡之日。闻有一名武曾经阃帅之人也。居丧在乡。忽有京客来吊者。既受吊。与之相对叙话。颇慇勤。杂以谐谑。其人既去。傍人问其为谁。曰不知也。何姓。曰不知也。名谁。曰不知也。居何地。曰不知也。然则果以为谁某而与之叙话。若是慇勤耶。曰只是字某也云云。盖所谓武弁之射亭友也。凡京中武弁之习艺于射亭者。操弓矢而出。望见有张帿之家。则辄往而赴之。射亭许多射夫之中。或有曾与之相面者。则揖而礼之。因与之为耦而射之。初不问其张帿之家之为谁某之家。张帿之家。亦不问其人之为谁某。凡诸射夫。亦不能自相谙悉。只是久久逐日相从。颜情自然稔熟。因成亲切之朋友矣。惟其如是。故不相知其为何姓何名何地居生。而随众口而呼之。所知者字而已。此所谓武弁之射亭友也。余在南乡之日。从游师友之间。如鹅川朴丈,沧溪林丈,咸平安进士,罗州罗仁卿,仁同申明仲,西湖崔复初诸人。相知之分。各有浅深。而莫不以道义相期。过失相规。切磋讲磨。久而不厌。自以为朋友居人伦之一。其道固应如此也。及来湖西之后数十年之间。其所与相知者。皆是相面于函丈坐上。
右。自然逢其源。非有意安排也。余昔在南乡之日。闻有一名武曾经阃帅之人也。居丧在乡。忽有京客来吊者。既受吊。与之相对叙话。颇慇勤。杂以谐谑。其人既去。傍人问其为谁。曰不知也。何姓。曰不知也。名谁。曰不知也。居何地。曰不知也。然则果以为谁某而与之叙话。若是慇勤耶。曰只是字某也云云。盖所谓武弁之射亭友也。凡京中武弁之习艺于射亭者。操弓矢而出。望见有张帿之家。则辄往而赴之。射亭许多射夫之中。或有曾与之相面者。则揖而礼之。因与之为耦而射之。初不问其张帿之家之为谁某之家。张帿之家。亦不问其人之为谁某。凡诸射夫。亦不能自相谙悉。只是久久逐日相从。颜情自然稔熟。因成亲切之朋友矣。惟其如是。故不相知其为何姓何名何地居生。而随众口而呼之。所知者字而已。此所谓武弁之射亭友也。余在南乡之日。从游师友之间。如鹅川朴丈,沧溪林丈,咸平安进士,罗州罗仁卿,仁同申明仲,西湖崔复初诸人。相知之分。各有浅深。而莫不以道义相期。过失相规。切磋讲磨。久而不厌。自以为朋友居人伦之一。其道固应如此也。及来湖西之后数十年之间。其所与相知者。皆是相面于函丈坐上。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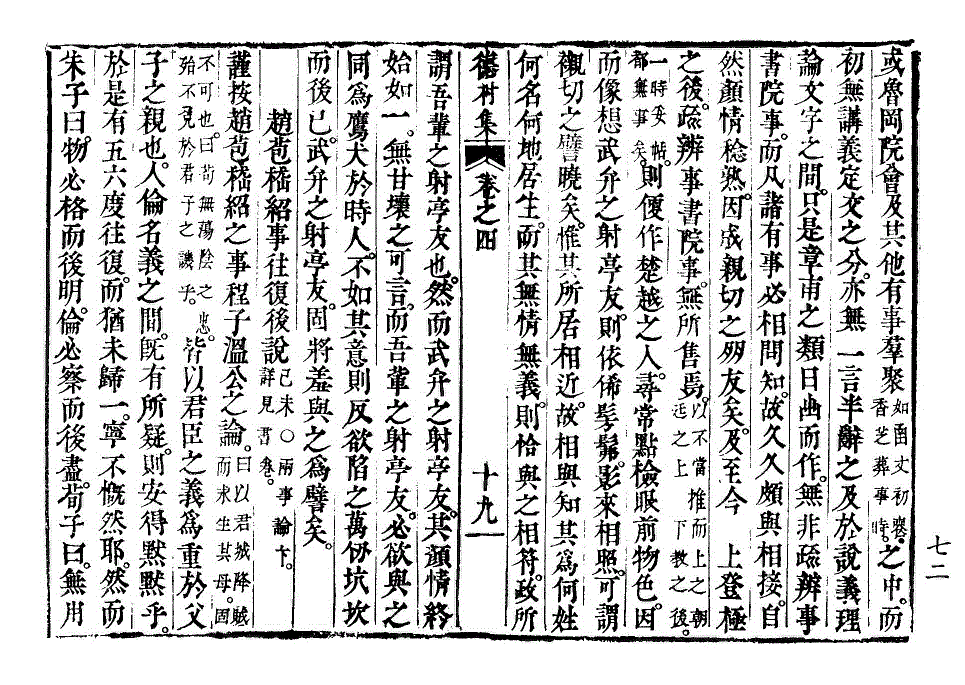 或鲁冈院会及其他有事群聚(如函丈初丧,香芝葬事时。)之中。而初无讲义定交之分。亦无一言半辞之及于说义理论文字之间。只是章甫之类日出而作。无非疏辨事书院事。而凡诸有事必相问知。故久久颇与相接。自然颜情稔熟。因成亲切之朋友矣。及至今 上登极之后。疏辨事书院事。无所售焉。(以不当推而上之朝廷之上 下教之后。一时妥帖。都无事矣。)则便作楚越之人。寻常点检眼前物色。因而像想武弁之射亭友。则依俙髣髴。影来相照。可谓衬切之譬晓矣。惟其所居相近。故相与知其为何姓何名何地居生。而其无情无义。则恰与之相符。政所谓吾辈之射亭友也。然而武弁之射亭友。其颜情终始如一。无甘坏之可言。而吾辈之射亭友。必欲与之同为鹰犬于时人。不如其意则反欲陷之万仞坑坎而后已。武弁之射亭友。固将羞与之为譬矣。
或鲁冈院会及其他有事群聚(如函丈初丧,香芝葬事时。)之中。而初无讲义定交之分。亦无一言半辞之及于说义理论文字之间。只是章甫之类日出而作。无非疏辨事书院事。而凡诸有事必相问知。故久久颇与相接。自然颜情稔熟。因成亲切之朋友矣。及至今 上登极之后。疏辨事书院事。无所售焉。(以不当推而上之朝廷之上 下教之后。一时妥帖。都无事矣。)则便作楚越之人。寻常点检眼前物色。因而像想武弁之射亭友。则依俙髣髴。影来相照。可谓衬切之譬晓矣。惟其所居相近。故相与知其为何姓何名何地居生。而其无情无义。则恰与之相符。政所谓吾辈之射亭友也。然而武弁之射亭友。其颜情终始如一。无甘坏之可言。而吾辈之射亭友。必欲与之同为鹰犬于时人。不如其意则反欲陷之万仞坑坎而后已。武弁之射亭友。固将羞与之为譬矣。赵苞嵇绍事往复后说(己未○两事论卞。详见书卷。)
谨按赵苞,嵇绍之事程子温公之论。(曰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固不可也。曰苟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皆以君臣之义为重于父子之亲也。人伦名义之间。既有所疑。则安得默默乎。于是有五六度往复。而犹未归一。宁不慨然耶。然而朱子曰。物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荀子曰。无用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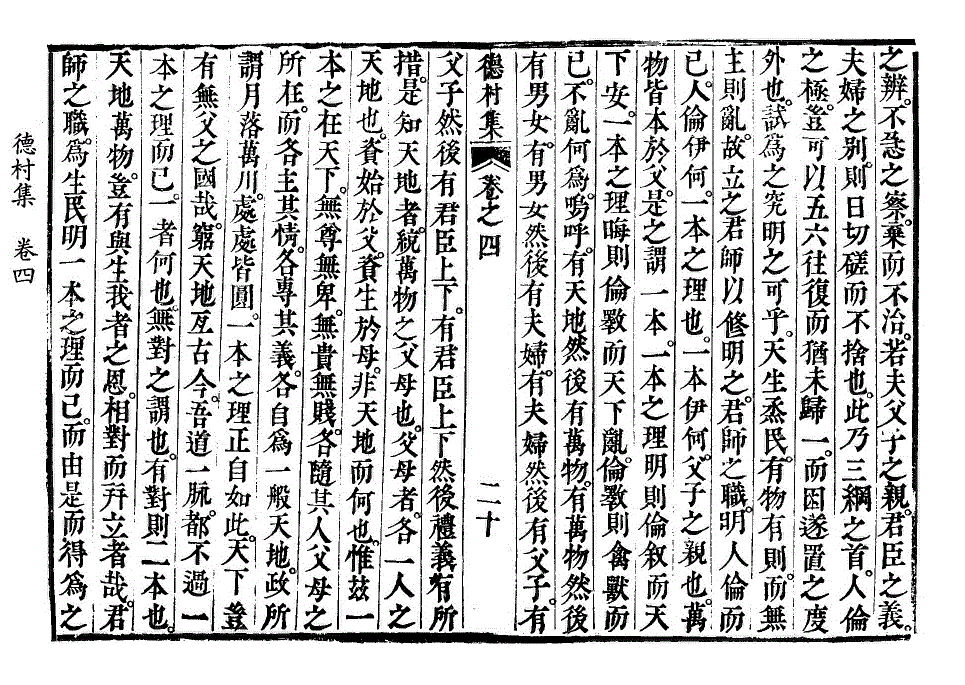 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此乃三纲之首。人伦之极。岂可以五六往复而犹未归一。而因遂置之度外也。试为之究明之可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而无主则乱。故立之君师以修明之。君师之职。明人伦而已。人伦伊何。一本之理也。一本伊何。父子之亲也。万物皆本于父。是之谓一本。一本之理明则伦叙而天下安。一本之理晦则伦斁而天下乱。伦斁则禽兽而已。不乱何为。呜呼。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有君臣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是知天地者。统万物之父母也。父母者。各一人之天地也。资始于父。资生于母。非天地而何也。惟玆一本之在天下。无尊无卑。无贵无贱。各随其人父母之所在。而各主其情。各专其义。各自为一般天地。政所谓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一本之理正自如此。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穷天地亘古今。吾道一脉。都不过一本之理而已。一者何也。无对之谓也。有对则二本也。天地万物。岂有与生我者之恩。相对而并立者哉。君师之职。为生民明一本之理而已。而由是而得为之
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此乃三纲之首。人伦之极。岂可以五六往复而犹未归一。而因遂置之度外也。试为之究明之可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而无主则乱。故立之君师以修明之。君师之职。明人伦而已。人伦伊何。一本之理也。一本伊何。父子之亲也。万物皆本于父。是之谓一本。一本之理明则伦叙而天下安。一本之理晦则伦斁而天下乱。伦斁则禽兽而已。不乱何为。呜呼。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有君臣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是知天地者。统万物之父母也。父母者。各一人之天地也。资始于父。资生于母。非天地而何也。惟玆一本之在天下。无尊无卑。无贵无贱。各随其人父母之所在。而各主其情。各专其义。各自为一般天地。政所谓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一本之理正自如此。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穷天地亘古今。吾道一脉。都不过一本之理而已。一者何也。无对之谓也。有对则二本也。天地万物。岂有与生我者之恩。相对而并立者哉。君师之职。为生民明一本之理而已。而由是而得为之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3L 页
 生之族焉。由是而得为之方其丧焉。既曰族。又曰方。所以明一本之理也。所以明无对之义也。孟子曰。瞽叟杀人。舜视弃天下。犹弃弊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邵子曰。圣人虽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爱。此所谓一本之理也。此所谓无对之义也。其君则不以天下。易其天性之爱。其臣则为君之一城而杀其母。抑将置其身于何地耶。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圣人之所同也。在其身则不忍为得天下而杀一不辜。而于其臣则许其为保一城而杀其母。是果近于情否耶。一本之理。无对之义。果如是耶。今且直将君之身与母之身相对而秤之。其斤两之轻重。当如何耶。准之以一本之理。不较明矣。况于以君之一城。较之于母之身。则又当如何耶。以是而观。则程子温公之论。其于人伦名义之间。不亦未安之甚乎。此小子之愤悱而欲为之启发者也。噫。自秦讫今上下数千年来。如此等事。此外又不可一二数计。(王莽之纂汉。分书年号于编年之下。其叙事。书莽之名。其死。书斩首于渐台。此弑君之贼也。安庆绪之杀禄山。史朝义之杀思明。俱是子杀父。而去父字子字。直书某杀某。禄山,思明。皆弑君之贼也。至于扬广之立也。大书炀帝大业元年于编年之首。其下几年。亦皆大书。其叙事。以帝书之。韦福嗣之败死。书以伏诛。其见杀于宇文化及。书以弑其君。此弑父之贼也。胡致
生之族焉。由是而得为之方其丧焉。既曰族。又曰方。所以明一本之理也。所以明无对之义也。孟子曰。瞽叟杀人。舜视弃天下。犹弃弊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邵子曰。圣人虽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爱。此所谓一本之理也。此所谓无对之义也。其君则不以天下。易其天性之爱。其臣则为君之一城而杀其母。抑将置其身于何地耶。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圣人之所同也。在其身则不忍为得天下而杀一不辜。而于其臣则许其为保一城而杀其母。是果近于情否耶。一本之理。无对之义。果如是耶。今且直将君之身与母之身相对而秤之。其斤两之轻重。当如何耶。准之以一本之理。不较明矣。况于以君之一城。较之于母之身。则又当如何耶。以是而观。则程子温公之论。其于人伦名义之间。不亦未安之甚乎。此小子之愤悱而欲为之启发者也。噫。自秦讫今上下数千年来。如此等事。此外又不可一二数计。(王莽之纂汉。分书年号于编年之下。其叙事。书莽之名。其死。书斩首于渐台。此弑君之贼也。安庆绪之杀禄山。史朝义之杀思明。俱是子杀父。而去父字子字。直书某杀某。禄山,思明。皆弑君之贼也。至于扬广之立也。大书炀帝大业元年于编年之首。其下几年。亦皆大书。其叙事。以帝书之。韦福嗣之败死。书以伏诛。其见杀于宇文化及。书以弑其君。此弑父之贼也。胡致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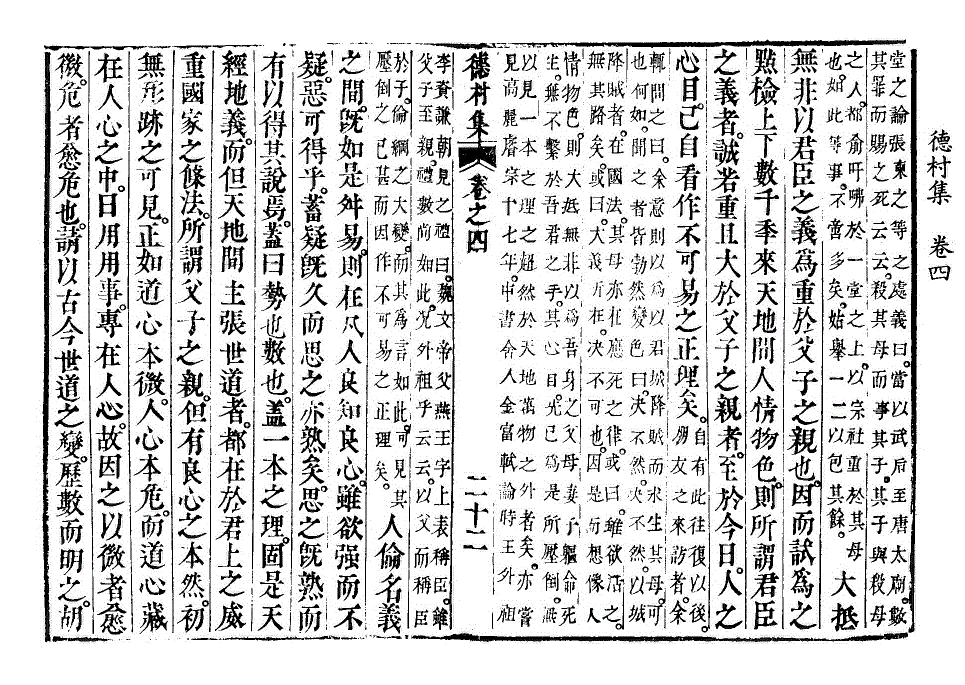 堂之论张柬之等之处义曰。当以武后至唐太庙。数其罪而赐之死云云。杀其母而事其子。其子与杀母之人。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以宗社重于其母也。如此等事。不啻多矣。姑举一二以包其馀。)大抵无非以君臣之义为重于父子之亲也。因而试为之点检上下数千年来天地间人情物色。则所谓君臣之义者。诚若重且大于父子之亲者。至于今日。人之心目。已自看作不可易之正理矣。(自有此往复以后。朋友之来访者。余辄问之曰。余意则以为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可也何如。闻之者皆勃然变色曰。决不然。决不然。以城降贼者。在国法。其母亦在应死之律。或曰。虽欲活之。无其路矣。或曰。大义所在。决不可也。因是而想像人情物色。则大抵无非以为吾身之父母妻子躯命死生。无不系于吾君之手。其心目。先已为是所压倒。无以见一本之理之超然于天地万物之外者矣。亦尝见高丽睿宗十七年。中书舍人金富轼论时王外祖李资谦朝见之礼曰。魏文帝父燕王宇上表称臣。虽父子至亲。礼数尚如此。况外祖乎云云。以父而称臣于子。伦纲之大变。而其为言如此。可见其压倒之已甚而因作不可易之正理矣。)人伦名义之间。既如是舛易。则在凡人良知良心。虽欲强而不疑。恶可得乎。蓄疑既久而思之亦熟矣。思之既熟而有以得其说焉。盖曰势也数也。盖一本之理。固是天经地义。而但天地间主张世道者。都在于君上之威重国家之条法。所谓父子之亲。但有良心之本然。初无形迹之可见。正如道心本微。人心本危。而道心藏在人心之中。日用用事。专在人心。故因之以微者愈微。危者愈危也。请以古今世道之变。历数而明之。胡
堂之论张柬之等之处义曰。当以武后至唐太庙。数其罪而赐之死云云。杀其母而事其子。其子与杀母之人。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以宗社重于其母也。如此等事。不啻多矣。姑举一二以包其馀。)大抵无非以君臣之义为重于父子之亲也。因而试为之点检上下数千年来天地间人情物色。则所谓君臣之义者。诚若重且大于父子之亲者。至于今日。人之心目。已自看作不可易之正理矣。(自有此往复以后。朋友之来访者。余辄问之曰。余意则以为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可也何如。闻之者皆勃然变色曰。决不然。决不然。以城降贼者。在国法。其母亦在应死之律。或曰。虽欲活之。无其路矣。或曰。大义所在。决不可也。因是而想像人情物色。则大抵无非以为吾身之父母妻子躯命死生。无不系于吾君之手。其心目。先已为是所压倒。无以见一本之理之超然于天地万物之外者矣。亦尝见高丽睿宗十七年。中书舍人金富轼论时王外祖李资谦朝见之礼曰。魏文帝父燕王宇上表称臣。虽父子至亲。礼数尚如此。况外祖乎云云。以父而称臣于子。伦纲之大变。而其为言如此。可见其压倒之已甚而因作不可易之正理矣。)人伦名义之间。既如是舛易。则在凡人良知良心。虽欲强而不疑。恶可得乎。蓄疑既久而思之亦熟矣。思之既熟而有以得其说焉。盖曰势也数也。盖一本之理。固是天经地义。而但天地间主张世道者。都在于君上之威重国家之条法。所谓父子之亲。但有良心之本然。初无形迹之可见。正如道心本微。人心本危。而道心藏在人心之中。日用用事。专在人心。故因之以微者愈微。危者愈危也。请以古今世道之变。历数而明之。胡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4L 页
 致堂论经权之说。以禹之传子谓之权。而并数于舜之不告而娶。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周公之杀管叔。仲尼之出妻。盖经者常也。常者常有之事也。权者变也。变者不常有之事也。然而所谓经者。尧舜之后至今数千年来。不复有焉。所谓权者。自夏讫今。因而永作常有之事焉。此乃世道之一大变。而一大变之后。终不能复焉。其故何也。韩文公对禹问政论此事。其言曰。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以守法。此即所谓势也数也。势即时势也。数即气数也。即时势气数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谓天地之常经。如隔前天地事矣。由是而禅授之事。谓之官天下。传子之事。谓之家天下。官天下者。公天下也。家天下者。私天下也。公天下者。以天下。为天下人公共之物。而惟以厚民生明人伦为主。所谓以一人治天下也。私天下者。以天下。为一己私有之物。而惟以享宗庙保子孙为计。所谓以天下奉一人也。宗庙享子孙保。固是天子之孝。而乃家天下以后事也。官天下以前。则只是代天理物之意而已。邵子之经世书。统论天地之大时势大气数。不啻明矣。有曰
致堂论经权之说。以禹之传子谓之权。而并数于舜之不告而娶。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周公之杀管叔。仲尼之出妻。盖经者常也。常者常有之事也。权者变也。变者不常有之事也。然而所谓经者。尧舜之后至今数千年来。不复有焉。所谓权者。自夏讫今。因而永作常有之事焉。此乃世道之一大变。而一大变之后。终不能复焉。其故何也。韩文公对禹问政论此事。其言曰。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以守法。此即所谓势也数也。势即时势也。数即气数也。即时势气数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谓天地之常经。如隔前天地事矣。由是而禅授之事。谓之官天下。传子之事。谓之家天下。官天下者。公天下也。家天下者。私天下也。公天下者。以天下。为天下人公共之物。而惟以厚民生明人伦为主。所谓以一人治天下也。私天下者。以天下。为一己私有之物。而惟以享宗庙保子孙为计。所谓以天下奉一人也。宗庙享子孙保。固是天子之孝。而乃家天下以后事也。官天下以前。则只是代天理物之意而已。邵子之经世书。统论天地之大时势大气数。不啻明矣。有曰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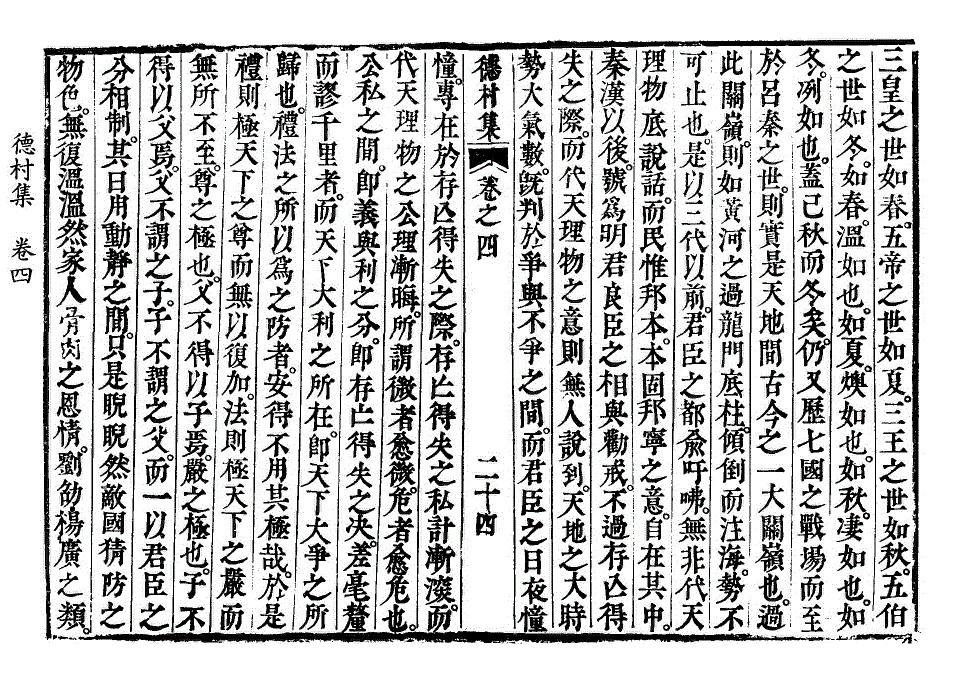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盖已秋而冬矣。仍又历七国之战场而至于吕秦之世。则实是天地间古今之一大关岭也。过此关岭。则如黄河之过龙门底柱。倾倒而注海。势不可止也。是以三代以前。君臣之都俞吁咈。无非代天理物底说话。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意。自在其中。秦汉以后。号为明君良臣之相与劝戒。不过存亡得失之际。而代天理物之意则无人说到。天地之大时势大气数。既判于争与不争之间。而君臣之日夜憧憧。专在于存亡得失之际。存亡得失之私计渐深。而代天理物之公理渐晦。所谓微者愈微。危者愈危也。公私之间。即义与利之分。即存亡得失之决。差毫釐而谬千里者。而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天下大争之所归也。礼法之所以为之防者。安得不用其极哉。于是礼则极天下之尊而无以复加。法则极天下之严而无所不至。尊之极也。父不得以子焉。严之极也。子不得以父焉。父不谓之子。子不谓之父。而一以君臣之分相制。其日用动静之间。只是睨睨然敌国猜防之物色。无复温温然家人骨肉之恩情。刘劭,杨广之类。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盖已秋而冬矣。仍又历七国之战场而至于吕秦之世。则实是天地间古今之一大关岭也。过此关岭。则如黄河之过龙门底柱。倾倒而注海。势不可止也。是以三代以前。君臣之都俞吁咈。无非代天理物底说话。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意。自在其中。秦汉以后。号为明君良臣之相与劝戒。不过存亡得失之际。而代天理物之意则无人说到。天地之大时势大气数。既判于争与不争之间。而君臣之日夜憧憧。专在于存亡得失之际。存亡得失之私计渐深。而代天理物之公理渐晦。所谓微者愈微。危者愈危也。公私之间。即义与利之分。即存亡得失之决。差毫釐而谬千里者。而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天下大争之所归也。礼法之所以为之防者。安得不用其极哉。于是礼则极天下之尊而无以复加。法则极天下之严而无所不至。尊之极也。父不得以子焉。严之极也。子不得以父焉。父不谓之子。子不谓之父。而一以君臣之分相制。其日用动静之间。只是睨睨然敌国猜防之物色。无复温温然家人骨肉之恩情。刘劭,杨广之类。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5L 页
 固所不论。号为明君谊辟。其父子兄弟之间。得免于自相屠戮者。盖无几矣。居君师之位。任人伦之责。而其所主张而张皇之者既如此。于是而所谓君臣之义者。俨然为名教之首。而父子之亲。风斯在下矣。到此则所谓微者。不但微而已。所谓危者。不但危而已。而所谓一本之理者。已泯然无迹矣。于是谅阴之礼废。易月之制作。而天下之通丧。不复闻于帝王之家矣。汉法之大不敬大不道。终至于虬须直视之崔琰。死于曹操之手。唐室之劫迁上皇之李辅国。晏然行呼唱于天子之侧。以所重在卫宗社也。天地之大时势大气数。到此更无一分馀地。为君之一城而杀其母。诚无足怪者矣。效死于杀父之家者。亦可免君子之讥矣。或曰。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以天子之父。而士师能执之。则尧舜之世。君臣之义。固已重于父子之亲矣。安在其明一本之理耶。余曰不然。当时瞽叟。在皋陶则君之父也。在大舜则其父也。于其君之父则直往执之。于其父则弃天下而窃负而逃。君臣父子。果孰轻而孰重欤。此即一本之理也。此即官天下。而天下为天下人公共之物也。若夫家天下以后。则汉之戾
固所不论。号为明君谊辟。其父子兄弟之间。得免于自相屠戮者。盖无几矣。居君师之位。任人伦之责。而其所主张而张皇之者既如此。于是而所谓君臣之义者。俨然为名教之首。而父子之亲。风斯在下矣。到此则所谓微者。不但微而已。所谓危者。不但危而已。而所谓一本之理者。已泯然无迹矣。于是谅阴之礼废。易月之制作。而天下之通丧。不复闻于帝王之家矣。汉法之大不敬大不道。终至于虬须直视之崔琰。死于曹操之手。唐室之劫迁上皇之李辅国。晏然行呼唱于天子之侧。以所重在卫宗社也。天地之大时势大气数。到此更无一分馀地。为君之一城而杀其母。诚无足怪者矣。效死于杀父之家者。亦可免君子之讥矣。或曰。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以天子之父。而士师能执之。则尧舜之世。君臣之义。固已重于父子之亲矣。安在其明一本之理耶。余曰不然。当时瞽叟。在皋陶则君之父也。在大舜则其父也。于其君之父则直往执之。于其父则弃天下而窃负而逃。君臣父子。果孰轻而孰重欤。此即一本之理也。此即官天下。而天下为天下人公共之物也。若夫家天下以后。则汉之戾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6H 页
 太子杀江充。而田千秋曰。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云。则何况天子之父乎。士师何敢执之乎。是则以天子之父故。藉力于天子之身。而得免于士师之诛。毕竟归重于君臣之义。而元不管于父子之亲也。今且先将孟子所谓执之而已。与夫所谓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与夫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此等训辞。潜心玩味。默识圣人之心。然后次看田千秋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一语。则古今势与数之推迁。而一本之理之因而埋没。庶可以领会于胸中矣。盖经权之舛易(时势气数)既久。本然之人情(一本之理)渐变。而自坐在里许。人自罔觉尔。苏子瞻诗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天下之理。正如是也。(呜呼。千载之下。像想当时物色。则赵苞之母。盖方身在俎上。刃拟于其颈。而视苞之进战而刃随以加矣。苞方腼然相对。政所谓人生到此。天道宁论者也。看到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之语。固已发立而胆轮囷矣。及至即时进战四字。不觉骨寒而气短。不忍见不忍读。此与手杀其母。岂此一毫间隔乎。所谓我往彼来间一人。不啻歇后语矣。于此而能忍之。则政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乃不忍于降贼者何耶。非人情所可测也。大源以程子固不可之训。为大纲道理云。而天下岂有为君之一城而杀母之大纲道理耶。闷塞闷塞。)
太子杀江充。而田千秋曰。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云。则何况天子之父乎。士师何敢执之乎。是则以天子之父故。藉力于天子之身。而得免于士师之诛。毕竟归重于君臣之义。而元不管于父子之亲也。今且先将孟子所谓执之而已。与夫所谓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与夫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此等训辞。潜心玩味。默识圣人之心。然后次看田千秋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一语。则古今势与数之推迁。而一本之理之因而埋没。庶可以领会于胸中矣。盖经权之舛易(时势气数)既久。本然之人情(一本之理)渐变。而自坐在里许。人自罔觉尔。苏子瞻诗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天下之理。正如是也。(呜呼。千载之下。像想当时物色。则赵苞之母。盖方身在俎上。刃拟于其颈。而视苞之进战而刃随以加矣。苞方腼然相对。政所谓人生到此。天道宁论者也。看到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之语。固已发立而胆轮囷矣。及至即时进战四字。不觉骨寒而气短。不忍见不忍读。此与手杀其母。岂此一毫间隔乎。所谓我往彼来间一人。不啻歇后语矣。于此而能忍之。则政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乃不忍于降贼者何耶。非人情所可测也。大源以程子固不可之训。为大纲道理云。而天下岂有为君之一城而杀母之大纲道理耶。闷塞闷塞。)揠苗说(己未)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毋若宋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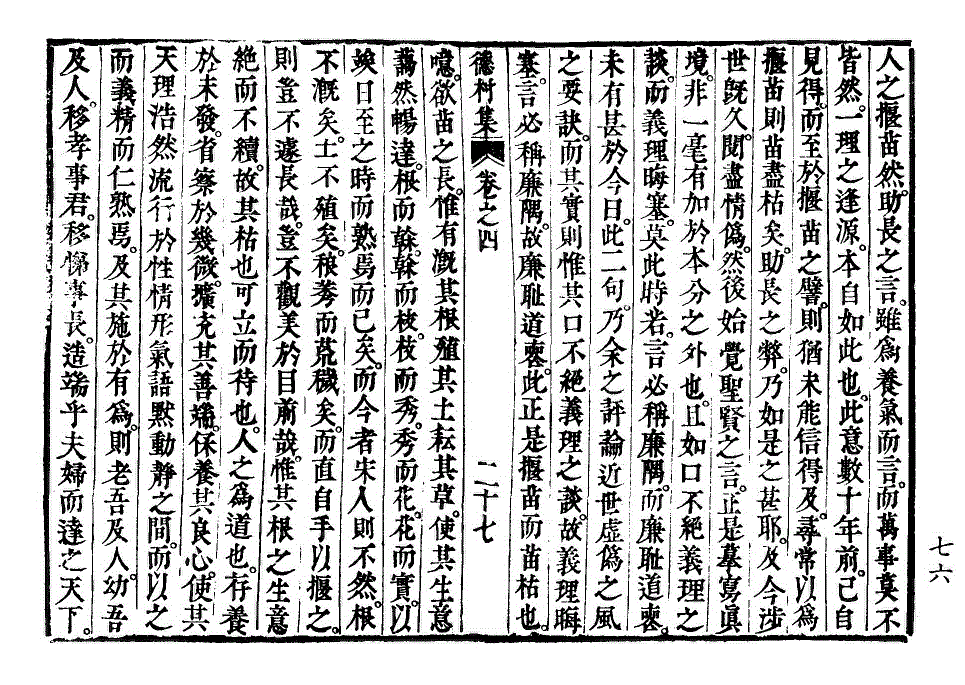 人之揠苗然。助长之言。虽为养气而言。而万事莫不皆然。一理之逢源。本自如此也。此意数十年前。已自见得。而至于揠苗之譬。则犹未能信得及。寻常以为揠苗则苗尽枯矣。助长之弊。乃如是之甚耶。及今涉世既久。阅尽情伪。然后始觉圣贤之言。正是摹写真境。非一毫有加于本分之外也。且如口不绝义理之谈。而义理晦塞。莫此时若。言必称廉隅。而廉耻道丧。未有甚于今日。此二句。乃余之评论近世虚伪之风之要诀。而其实则惟其口不绝义理之谈。故义理晦塞。言必称廉隅。故廉耻道丧。此正是揠苗而苗枯也。噫。欲苗之长。惟有溉其根殖其土耘其草。使其生意蔼然畅达。根而干。干而枝。枝而秀。秀而花。花而实。以俟日至之时而熟焉而已矣。而今者宋人则不然。根不溉矣。土不殖矣。稂莠而荒秽矣。而直自手以揠之。则岂不遽长哉。岂不观美于目前哉。惟其根之生意绝而不续。故其枯也可立而待也。人之为道也。存养于未发。省察于几微。扩充其善端。保养其良心。使其天理浩然流行于性情形气语默动静之间。而以之而义精而仁熟焉。及其施于有为。则老吾及人。幼吾及人。移孝事君。移悌事长。造端乎夫妇而达之天下。
人之揠苗然。助长之言。虽为养气而言。而万事莫不皆然。一理之逢源。本自如此也。此意数十年前。已自见得。而至于揠苗之譬。则犹未能信得及。寻常以为揠苗则苗尽枯矣。助长之弊。乃如是之甚耶。及今涉世既久。阅尽情伪。然后始觉圣贤之言。正是摹写真境。非一毫有加于本分之外也。且如口不绝义理之谈。而义理晦塞。莫此时若。言必称廉隅。而廉耻道丧。未有甚于今日。此二句。乃余之评论近世虚伪之风之要诀。而其实则惟其口不绝义理之谈。故义理晦塞。言必称廉隅。故廉耻道丧。此正是揠苗而苗枯也。噫。欲苗之长。惟有溉其根殖其土耘其草。使其生意蔼然畅达。根而干。干而枝。枝而秀。秀而花。花而实。以俟日至之时而熟焉而已矣。而今者宋人则不然。根不溉矣。土不殖矣。稂莠而荒秽矣。而直自手以揠之。则岂不遽长哉。岂不观美于目前哉。惟其根之生意绝而不续。故其枯也可立而待也。人之为道也。存养于未发。省察于几微。扩充其善端。保养其良心。使其天理浩然流行于性情形气语默动静之间。而以之而义精而仁熟焉。及其施于有为。则老吾及人。幼吾及人。移孝事君。移悌事长。造端乎夫妇而达之天下。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盖莫不本之吾身心以及于四海。而人皆知天下国家之皆本于吾身。又皆知吾心之为万化之原而位育之功成焉。尧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以此道也。今之为士者。异于是。其身心则姑不论。亦不知有其家。而直以卫斯道扶世教之言。作为好个题目。以为所谓道者。别有一个悬空独立。遇其人而托焉。如灵神之降于大巫。遂以其人为道之所存。以其人之家为吾道之家而身往卫焉。又自以为身既出入于吾道之家与吾道之一族。交游则亦不可全然不顾义理。于是发言举事。每将义理二字。作一目前榜子。而口不绝于谈头。以为此事虽未安于义理。而与吾道之家不相干涉。则无所妨也。若或有妨于吾道之家。则人将谓之何哉。乃力为之分解于人曰。吾之为此事。元非吾道之家之所知也。至于吾道之一族之家虽有悖义非理之事。而一切为之掩讳。令人不敢诃谪。恐或挨逼于吾道之家。凡有可以卫吾道之家者。虽欺君罔上之事。亦不惮身自蹈之。人或有言其不是者。则反以为无诚于吾道之家。而攻之不遗馀力。以是为义理之当然。此所谓口不绝义理之谈。而义理晦塞。莫此时若也。是则举一世而揠之。而举一世而
盖莫不本之吾身心以及于四海。而人皆知天下国家之皆本于吾身。又皆知吾心之为万化之原而位育之功成焉。尧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以此道也。今之为士者。异于是。其身心则姑不论。亦不知有其家。而直以卫斯道扶世教之言。作为好个题目。以为所谓道者。别有一个悬空独立。遇其人而托焉。如灵神之降于大巫。遂以其人为道之所存。以其人之家为吾道之家而身往卫焉。又自以为身既出入于吾道之家与吾道之一族。交游则亦不可全然不顾义理。于是发言举事。每将义理二字。作一目前榜子。而口不绝于谈头。以为此事虽未安于义理。而与吾道之家不相干涉。则无所妨也。若或有妨于吾道之家。则人将谓之何哉。乃力为之分解于人曰。吾之为此事。元非吾道之家之所知也。至于吾道之一族之家虽有悖义非理之事。而一切为之掩讳。令人不敢诃谪。恐或挨逼于吾道之家。凡有可以卫吾道之家者。虽欺君罔上之事。亦不惮身自蹈之。人或有言其不是者。则反以为无诚于吾道之家。而攻之不遗馀力。以是为义理之当然。此所谓口不绝义理之谈。而义理晦塞。莫此时若也。是则举一世而揠之。而举一世而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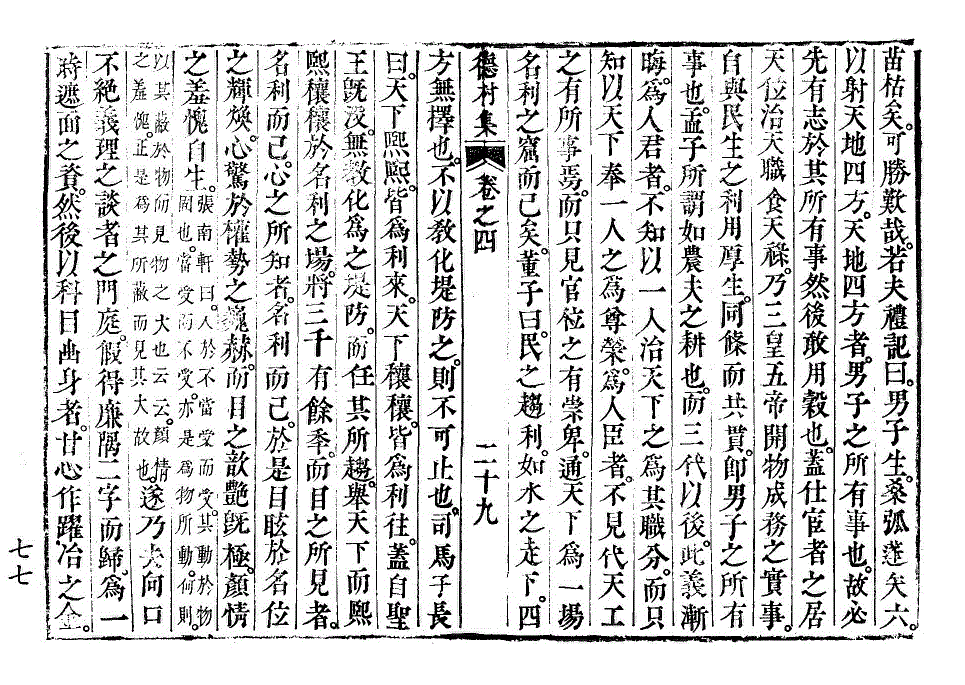 苗枯矣。可胜叹哉。若夫礼记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盖仕宦者之居天位治天职食天禄。乃三皇五帝开物成务之实事。自与民生之利用厚生。同条而共贯。即男子之所有事也。孟子所谓如农夫之耕也。而三代以后。此义渐晦。为人君者。不知以一人治天下之为其职分。而只知以天下奉一人之为尊荣。为人臣者。不见代天工之有所事焉。而只见官位之有崇卑。通天下为一场名利之窟而已矣。董子曰。民之趋利。如水之走下。四方无择也。不以教化堤防之。则不可止也。司马子长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穰穰。皆为利往。盖自圣王既没。无教化为之堤防。而任其所趋。举天下而熙熙穰穰于名利之场。将三千有馀年。而目之所见者。名利而已。心之所知者。名利而已。于是目眩于名位之辉焕。心惊于权势之巍赫。而目之歆艳既极。颜情之羞愧自生。(张南轩曰。人于不当受而受。其动于物固也。当受而不受。亦是为物所动。何则。以其蔽于物而见物之大也云云。颜情之羞愧。正是为其所蔽而见其大故也。)遂乃夫向口不绝义理之谈者之门庭。假得廉隅二字而归。为一时遮面之资。然后以科目出身者。甘心作跃冶之金。
苗枯矣。可胜叹哉。若夫礼记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盖仕宦者之居天位治天职食天禄。乃三皇五帝开物成务之实事。自与民生之利用厚生。同条而共贯。即男子之所有事也。孟子所谓如农夫之耕也。而三代以后。此义渐晦。为人君者。不知以一人治天下之为其职分。而只知以天下奉一人之为尊荣。为人臣者。不见代天工之有所事焉。而只见官位之有崇卑。通天下为一场名利之窟而已矣。董子曰。民之趋利。如水之走下。四方无择也。不以教化堤防之。则不可止也。司马子长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穰穰。皆为利往。盖自圣王既没。无教化为之堤防。而任其所趋。举天下而熙熙穰穰于名利之场。将三千有馀年。而目之所见者。名利而已。心之所知者。名利而已。于是目眩于名位之辉焕。心惊于权势之巍赫。而目之歆艳既极。颜情之羞愧自生。(张南轩曰。人于不当受而受。其动于物固也。当受而不受。亦是为物所动。何则。以其蔽于物而见物之大也云云。颜情之羞愧。正是为其所蔽而见其大故也。)遂乃夫向口不绝义理之谈者之门庭。假得廉隅二字而归。为一时遮面之资。然后以科目出身者。甘心作跃冶之金。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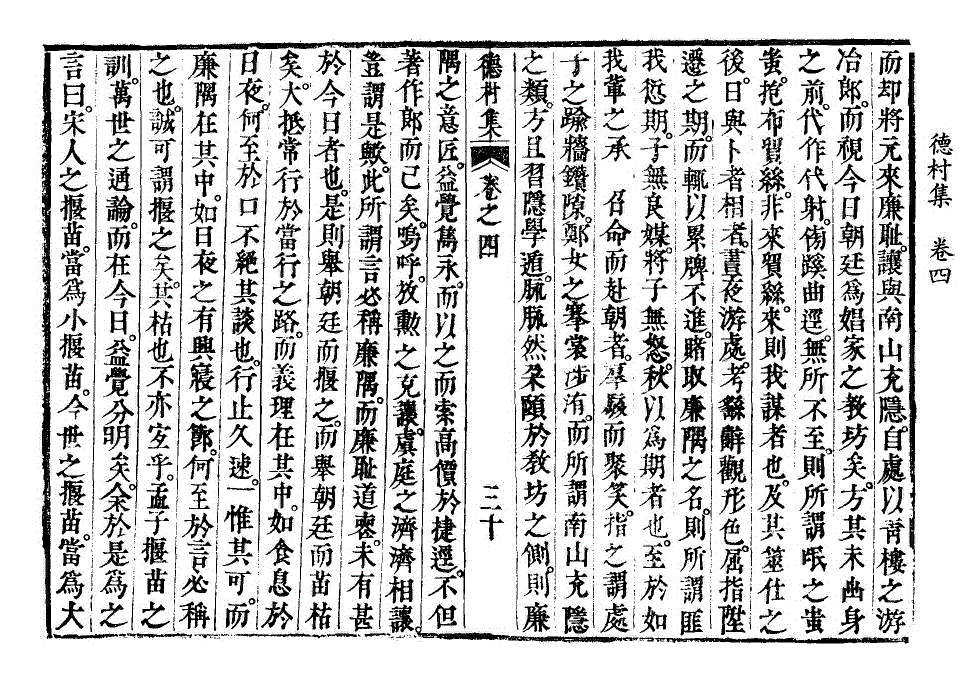 而却将元来廉耻。让与南山充隐。自处以青楼之游冶郎。而视今日朝廷为娼家之教坊矣。方其未出身之前。代作代射。傍蹊曲径。无所不至。则所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非来贸丝。来则我谋者也。及其筮仕之后。日与卜者相者。昼夜游处。考繇辞观形色。屈指升迁之期。而辄以累牌不进。赌取廉隅之名。则所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者也。至于如我辈之承 召命而赴朝者。群骇而聚笑。指之谓处子之踰墙钻隙。郑女之搴裳涉洧。而所谓南山充隐之类。方且习隐学遁。脉脉然朵颐于教坊之侧。则廉隅之意匠。益觉隽永。而以之而索高价于捷径。不但著作郎而已矣。呜呼。放勋之克让。虞庭之济济相让。岂谓是欤。此所谓言必称廉隅。而廉耻道丧。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是则举朝廷而揠之。而举朝廷而苗枯矣。大抵常行于当行之路。而义理在其中。如食息于日夜。何至于口不绝其谈也。行止久速。一惟其可。而廉隅在其中。如日夜之有兴寝之节。何至于言必称之也。诚可谓揠之矣。其枯也不亦宜乎。孟子揠苗之训。万世之通论。而在今日。益觉分明矣。余于是为之言曰。宋人之揠苗。当为小揠苗。今世之揠苗。当为大
而却将元来廉耻。让与南山充隐。自处以青楼之游冶郎。而视今日朝廷为娼家之教坊矣。方其未出身之前。代作代射。傍蹊曲径。无所不至。则所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非来贸丝。来则我谋者也。及其筮仕之后。日与卜者相者。昼夜游处。考繇辞观形色。屈指升迁之期。而辄以累牌不进。赌取廉隅之名。则所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者也。至于如我辈之承 召命而赴朝者。群骇而聚笑。指之谓处子之踰墙钻隙。郑女之搴裳涉洧。而所谓南山充隐之类。方且习隐学遁。脉脉然朵颐于教坊之侧。则廉隅之意匠。益觉隽永。而以之而索高价于捷径。不但著作郎而已矣。呜呼。放勋之克让。虞庭之济济相让。岂谓是欤。此所谓言必称廉隅。而廉耻道丧。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是则举朝廷而揠之。而举朝廷而苗枯矣。大抵常行于当行之路。而义理在其中。如食息于日夜。何至于口不绝其谈也。行止久速。一惟其可。而廉隅在其中。如日夜之有兴寝之节。何至于言必称之也。诚可谓揠之矣。其枯也不亦宜乎。孟子揠苗之训。万世之通论。而在今日。益觉分明矣。余于是为之言曰。宋人之揠苗。当为小揠苗。今世之揠苗。当为大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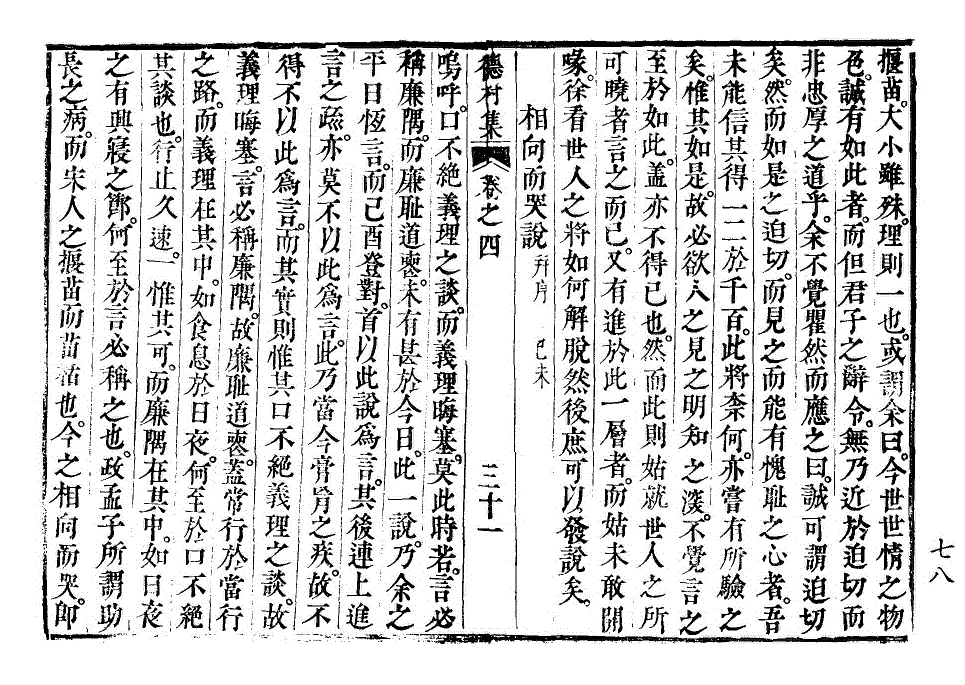 揠苗。大小虽殊。理则一也。或谓余曰。今世世情之物色。诚有如此者。而但君子之辞令。无乃近于迫切而非忠厚之道乎。余不觉瞿然而应之曰。诚可谓迫切矣。然而如是之迫切。而见之而能有愧耻之心者。吾未能信其得一二于千百。此将柰何。亦尝有所验之矣。惟其如是。故必欲人之见之明知之深。不觉言之至于如此。盖亦不得已也。然而此则姑就世人之所可晓者言之而已。又有进于此一层者。而姑未敢开喙。徐看世人之将如何解脱然后庶可以发说矣。
揠苗。大小虽殊。理则一也。或谓余曰。今世世情之物色。诚有如此者。而但君子之辞令。无乃近于迫切而非忠厚之道乎。余不觉瞿然而应之曰。诚可谓迫切矣。然而如是之迫切。而见之而能有愧耻之心者。吾未能信其得一二于千百。此将柰何。亦尝有所验之矣。惟其如是。故必欲人之见之明知之深。不觉言之至于如此。盖亦不得已也。然而此则姑就世人之所可晓者言之而已。又有进于此一层者。而姑未敢开喙。徐看世人之将如何解脱然后庶可以发说矣。相向而哭说(并序○己未)
呜呼。口不绝义理之谈。而义理晦塞。莫此时若。言必称廉隅。而廉耻道丧。未有甚于今日。此一说。乃余之平日恒言。而己酉登对。首以此说为言。其后连上进言之疏。亦莫不以此为言。此乃当今膏肓之疾。故不得不以此为言。而其实则惟其口不绝义理之谈。故义理晦塞。言必称廉隅。故廉耻道丧。盖常行于当行之路。而义理在其中。如食息于日夜。何至于口不绝其谈也。行止久速。一惟其可。而廉隅在其中。如日夜之有兴寝之节。何至于言必称之也。政孟子所谓助长之病。而宋人之揠苗而苗枯也。今之相向而哭。即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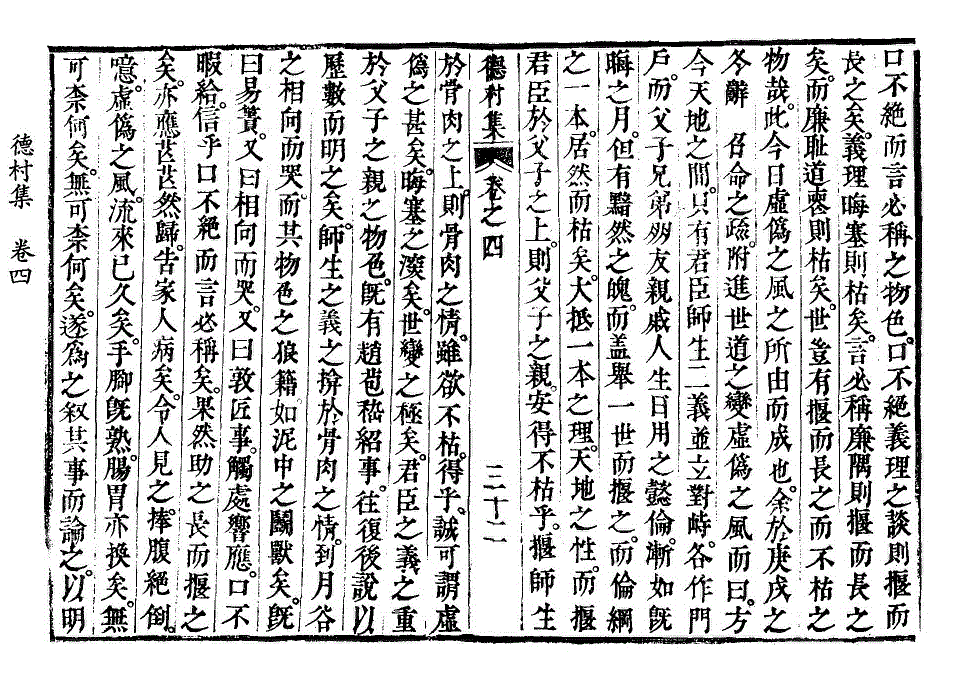 口不绝而言必称之物色。口不绝义理之谈则揠而长之矣。义理晦塞则枯矣。言必称廉隅则揠而长之矣。而廉耻道丧则枯矣。世岂有揠而长之而不枯之物哉。此今日虚伪之风之所由而成也。余于庚戌之冬辞 召命之疏。附进世道之变虚伪之风而曰。方今天地之间。只有君臣师生二义并立对峙。各作门户。而父子兄弟朋友亲戚人生日用之懿伦。渐如既晦之月。但有黯然之魄。而盖举一世而揠之。而伦纲之一本。居然而枯矣。大抵一本之理。天地之性。而揠君臣于父子之上。则父子之亲。安得不枯乎。揠师生于骨肉之上。则骨肉之情。虽欲不枯。得乎。诚可谓虚伪之甚矣。晦塞之深矣。世变之极矣。君臣之义之重于父子之亲之物色。既有赵苞嵇绍事。往复后说以历数而明之矣。师生之义之掩于骨肉之情。到月谷之相向而哭。而其物色之狼藉。如泥中之斗兽矣。既曰易箦。又曰相向而哭。又曰敦匠事。触处响应。口不暇给。信乎口不绝而言必称矣。果然助之长而揠之矣。亦应芒芒然归。告家人病矣。令人见之。捧腹绝倒。噫。虚伪之风。流来已久矣。手脚既熟。肠胃亦换矣。无可柰何矣。无可柰何矣。遂为之叙其事而论之。以明
口不绝而言必称之物色。口不绝义理之谈则揠而长之矣。义理晦塞则枯矣。言必称廉隅则揠而长之矣。而廉耻道丧则枯矣。世岂有揠而长之而不枯之物哉。此今日虚伪之风之所由而成也。余于庚戌之冬辞 召命之疏。附进世道之变虚伪之风而曰。方今天地之间。只有君臣师生二义并立对峙。各作门户。而父子兄弟朋友亲戚人生日用之懿伦。渐如既晦之月。但有黯然之魄。而盖举一世而揠之。而伦纲之一本。居然而枯矣。大抵一本之理。天地之性。而揠君臣于父子之上。则父子之亲。安得不枯乎。揠师生于骨肉之上。则骨肉之情。虽欲不枯。得乎。诚可谓虚伪之甚矣。晦塞之深矣。世变之极矣。君臣之义之重于父子之亲之物色。既有赵苞嵇绍事。往复后说以历数而明之矣。师生之义之掩于骨肉之情。到月谷之相向而哭。而其物色之狼藉。如泥中之斗兽矣。既曰易箦。又曰相向而哭。又曰敦匠事。触处响应。口不暇给。信乎口不绝而言必称矣。果然助之长而揠之矣。亦应芒芒然归。告家人病矣。令人见之。捧腹绝倒。噫。虚伪之风。流来已久矣。手脚既熟。肠胃亦换矣。无可柰何矣。无可柰何矣。遂为之叙其事而论之。以明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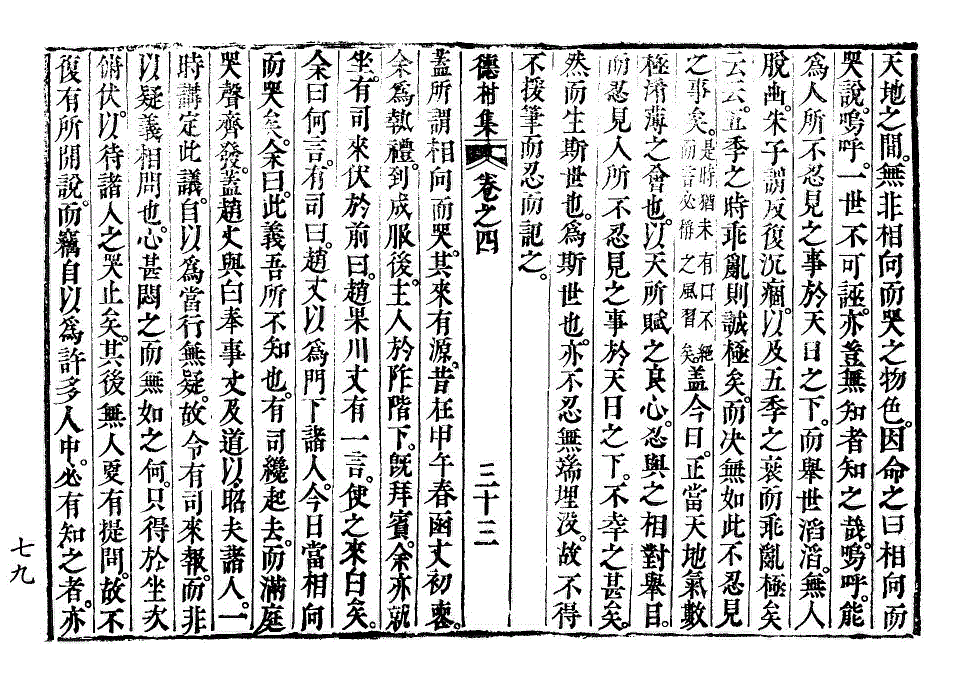 天地之间。无非相向而哭之物色。因命之曰相向而哭说。呜呼。一世不可诬。亦岂无知者知之哉。呜呼。能为人所不忍见之事于天日之下。而举世滔滔。无人脱出。朱子谓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乖乱极矣云云。五季之时乖乱则诚极矣。而决无如此不忍见之事矣。(是时犹未有口不绝而言必称之风习矣。)盖今日。正当天地气数极淆薄之会也。以天所赋之良心。忍与之相对举目。而忍见人所不忍见之事于天日之下。不幸之甚矣。然而生斯世也。为斯世也。亦不忍无端埋没。故不得不援笔而忍而记之。
天地之间。无非相向而哭之物色。因命之曰相向而哭说。呜呼。一世不可诬。亦岂无知者知之哉。呜呼。能为人所不忍见之事于天日之下。而举世滔滔。无人脱出。朱子谓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乖乱极矣云云。五季之时乖乱则诚极矣。而决无如此不忍见之事矣。(是时犹未有口不绝而言必称之风习矣。)盖今日。正当天地气数极淆薄之会也。以天所赋之良心。忍与之相对举目。而忍见人所不忍见之事于天日之下。不幸之甚矣。然而生斯世也。为斯世也。亦不忍无端埋没。故不得不援笔而忍而记之。盖所谓相向而哭。其来有源。昔在甲午春函丈初丧。余为执礼。到成服后。主人于阼阶下。既拜宾。余亦就坐。有司来伏于前曰。赵果川丈有一言。使之来白矣。余曰何言。有司曰。赵丈以为门下诸人。今日当相向而哭矣。余曰。此义吾所不知也。有司才起去。而满庭哭声齐发。盖赵丈与白奉事丈及道以,昭夫诸人。一时讲定此议。自以为当行无疑。故令有司来报。而非以疑义相问也。心甚闷之而无如之何。只得于坐次俯伏。以待诸人之哭止矣。其后无人更有提问。故不复有所开说。而窃自以为许多人中。必有知之者。亦
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80H 页
 必有能辨之者。至三月香芝葬事时下棺后。既皆临圹而哭。主人哭尽哀而止。扶就幕次。方劝歠粥。而忽又有司来告曰。赵果川丈使白于执礼。请相向而哭。余于是瞿然回顾。则赵丈尚在临圹之位。哭声甚哀。涕泪交横。时时举头而言曰。白于执礼。请相向而哭。余时与韩监司(配夏),李咨议(泰寿),大源,子厚诸人同坐。余乃向诸人言曰。向者初丧时。事出苍黄。未及分明解说。以致一番误著。今则不得不略有开说矣。孔门弟子以散在各国之人。而同事一师。一朝山颓梁坏。奄过三年。无可依矣。无可仰矣。各治其任。各还其家。此时此别。当何为心。情发于中。不觉痛哭。此所谓相向而哭也。今日吾辈则自初丧至今日。朝夕朔望之哭。惟意所宜。而今又临圹而哭。又将反虞而哭矣。又将连有朝夕之哭矣。此时主人哭已尽哀而止。方歠粥于幕次。而吾辈别与相向而哭。其义何居云。则诸人皆以为然。有司以此意言于赵丈而止其哭而罢矣。盖此事本非人之必待费力致思而后可知。只是稍解文理。(孟子本文)平心读书者。人人之所可知也。自常人见之。其羞愧忸怩。实难举颜于人。而赵丈倡之。众人和附。无一人别其是非。其后丁酉春白奉事丈
必有能辨之者。至三月香芝葬事时下棺后。既皆临圹而哭。主人哭尽哀而止。扶就幕次。方劝歠粥。而忽又有司来告曰。赵果川丈使白于执礼。请相向而哭。余于是瞿然回顾。则赵丈尚在临圹之位。哭声甚哀。涕泪交横。时时举头而言曰。白于执礼。请相向而哭。余时与韩监司(配夏),李咨议(泰寿),大源,子厚诸人同坐。余乃向诸人言曰。向者初丧时。事出苍黄。未及分明解说。以致一番误著。今则不得不略有开说矣。孔门弟子以散在各国之人。而同事一师。一朝山颓梁坏。奄过三年。无可依矣。无可仰矣。各治其任。各还其家。此时此别。当何为心。情发于中。不觉痛哭。此所谓相向而哭也。今日吾辈则自初丧至今日。朝夕朔望之哭。惟意所宜。而今又临圹而哭。又将反虞而哭矣。又将连有朝夕之哭矣。此时主人哭已尽哀而止。方歠粥于幕次。而吾辈别与相向而哭。其义何居云。则诸人皆以为然。有司以此意言于赵丈而止其哭而罢矣。盖此事本非人之必待费力致思而后可知。只是稍解文理。(孟子本文)平心读书者。人人之所可知也。自常人见之。其羞愧忸怩。实难举颜于人。而赵丈倡之。众人和附。无一人别其是非。其后丁酉春白奉事丈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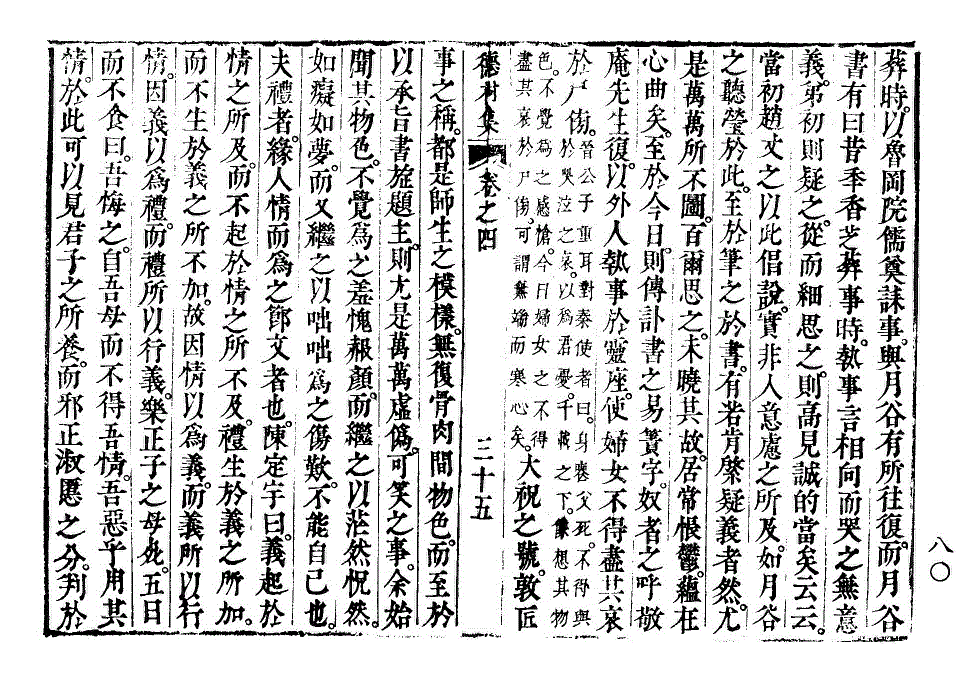 葬时。以鲁冈院儒奠诔事。与月谷有所往复。而月谷书有曰昔年香芝葬事时。执事言相向而哭之无意义。弟初则疑之。从而细思之。则高见诚的当矣云云。当初赵丈之以此倡说。实非人意虑之所及。如月谷之听莹于此。至于笔之于书。有若肯綮疑义者然。尤是万万所不图。百尔思之。未晓其故。居常怅郁。蕴在心曲矣。至于今日。则传讣书之易箦字。奴者之呼敬庵先生复。以外人执事于灵座。使妇女不得尽其哀于尸傍。(晋公子重耳对秦使者曰。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千载之下。像想其物色。不觉为之感怆。今日妇女之不得尽其哀于尸傍。可谓无端而寒心矣。)大祝之号。敦匠事之称。都是师生之模样。无复骨肉间物色。而至于以承旨书㫌题主。则尤是万万虚伪。可笑之事。余始闻其物色。不觉为之羞愧赧颜。而继之以茫然恍然。如痴如梦。而又继之以咄咄为之伤叹。不能自已也。夫礼者。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陈定宇曰。义起于情之所及。而不起于情之所不及。礼生于义之所加。而不生于义之所不加。故因情以为义。而义所以行情。因义以为礼。而礼所以行义。乐正子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其情。于此可以见君子之所养。而邪正淑慝之分。判于
葬时。以鲁冈院儒奠诔事。与月谷有所往复。而月谷书有曰昔年香芝葬事时。执事言相向而哭之无意义。弟初则疑之。从而细思之。则高见诚的当矣云云。当初赵丈之以此倡说。实非人意虑之所及。如月谷之听莹于此。至于笔之于书。有若肯綮疑义者然。尤是万万所不图。百尔思之。未晓其故。居常怅郁。蕴在心曲矣。至于今日。则传讣书之易箦字。奴者之呼敬庵先生复。以外人执事于灵座。使妇女不得尽其哀于尸傍。(晋公子重耳对秦使者曰。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千载之下。像想其物色。不觉为之感怆。今日妇女之不得尽其哀于尸傍。可谓无端而寒心矣。)大祝之号。敦匠事之称。都是师生之模样。无复骨肉间物色。而至于以承旨书㫌题主。则尤是万万虚伪。可笑之事。余始闻其物色。不觉为之羞愧赧颜。而继之以茫然恍然。如痴如梦。而又继之以咄咄为之伤叹。不能自已也。夫礼者。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陈定宇曰。义起于情之所及。而不起于情之所不及。礼生于义之所加。而不生于义之所不加。故因情以为义。而义所以行情。因义以为礼。而礼所以行义。乐正子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其情。于此可以见君子之所养。而邪正淑慝之分。判于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81H 页
 情与不情之间者。可谓懔然而寒心矣。情与不情。即诚伪之分。诚伪之分。即义与利之辨。而义与利之辨。孟子之告梁惠王宋牼。其说为何如云耶。苏老泉之辨奸论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于论王荆公。固不免为深文。而若通论天下之理。则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乐正子之五日不食。只是过情之礼。所谓毫釐之差。(曾子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酱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曾子之七日不食。情也。乐正子之五日不食。过于情也。苟非自以为悔。则孰知其五日之为过于情哉。此所谓毫釐之差也。)而才差失。便即悔之。悚然惩创于情与不情之间者。以毫釐之差。终至于千里之谬也。况于所谓不近人情者。元初之差。已不啻千里矣。尚何论谬之远近哉。主人哭尽哀而止。方歠粥于幕次。而门人则哀犹未尽。涕泪滂沱。不能收检。为人所扶。不能自持。必须别与相向而哭。然后方可以尽其情而泄其哀。求诸天理人情。为近耶远耶。此时主人之颜情。抑将置之何地耶。若使乐正子见之。当何以为心耶。呜呼。五伦无师生之目。师生本在朋友之伦。而今世之无朋友久矣。无朋友而有师生。假师生而做出朋友之名。(指之谓同志。称之谓朋友。)则元是人伦名教之外。而无非宣陵孝子之类也。相聚墟墓之间。假托圣
情与不情之间者。可谓懔然而寒心矣。情与不情。即诚伪之分。诚伪之分。即义与利之辨。而义与利之辨。孟子之告梁惠王宋牼。其说为何如云耶。苏老泉之辨奸论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于论王荆公。固不免为深文。而若通论天下之理。则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乐正子之五日不食。只是过情之礼。所谓毫釐之差。(曾子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酱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曾子之七日不食。情也。乐正子之五日不食。过于情也。苟非自以为悔。则孰知其五日之为过于情哉。此所谓毫釐之差也。)而才差失。便即悔之。悚然惩创于情与不情之间者。以毫釐之差。终至于千里之谬也。况于所谓不近人情者。元初之差。已不啻千里矣。尚何论谬之远近哉。主人哭尽哀而止。方歠粥于幕次。而门人则哀犹未尽。涕泪滂沱。不能收检。为人所扶。不能自持。必须别与相向而哭。然后方可以尽其情而泄其哀。求诸天理人情。为近耶远耶。此时主人之颜情。抑将置之何地耶。若使乐正子见之。当何以为心耶。呜呼。五伦无师生之目。师生本在朋友之伦。而今世之无朋友久矣。无朋友而有师生。假师生而做出朋友之名。(指之谓同志。称之谓朋友。)则元是人伦名教之外。而无非宣陵孝子之类也。相聚墟墓之间。假托圣德村先生集卷之四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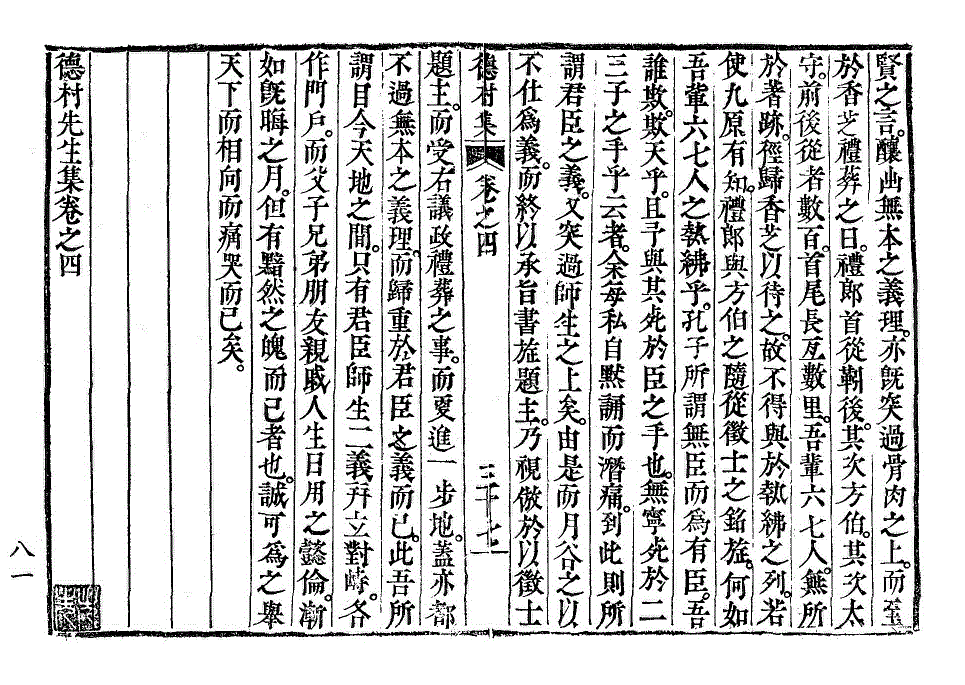 贤之言。酿出无本之义理。亦既突过骨肉之上。而至于香芝礼葬之日。礼郎首从靷后。其次方伯。其次太守。前后从者数百。首尾长亘数里。吾辈六七人。无所于著迹。径归香芝以待之。故不得与于执绋之列。若使九原有知。礼郎与方伯之随从徵士之铭㫌。何如吾辈六七人之执绋乎。孔子所谓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云者。余每私自默诵而潜痛。到此则所谓君臣之义。又突过师生之上矣。由是而月谷之以不仕为义。而终以承旨书㫌题主。乃视仿于以徵士题主。而受右议政礼葬之事。而更进一步地。盖亦都不过无本之义理。而归重于君臣之义而已。此吾所谓目今天地之间。只有君臣师生二义并立对峙。各作门户。而父子兄弟朋友亲戚人生日用之懿伦。渐如既晦之月。但有黯然之魄而已者也。诚可为之举天下而相向而痛哭而已矣。
贤之言。酿出无本之义理。亦既突过骨肉之上。而至于香芝礼葬之日。礼郎首从靷后。其次方伯。其次太守。前后从者数百。首尾长亘数里。吾辈六七人。无所于著迹。径归香芝以待之。故不得与于执绋之列。若使九原有知。礼郎与方伯之随从徵士之铭㫌。何如吾辈六七人之执绋乎。孔子所谓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云者。余每私自默诵而潜痛。到此则所谓君臣之义。又突过师生之上矣。由是而月谷之以不仕为义。而终以承旨书㫌题主。乃视仿于以徵士题主。而受右议政礼葬之事。而更进一步地。盖亦都不过无本之义理。而归重于君臣之义而已。此吾所谓目今天地之间。只有君臣师生二义并立对峙。各作门户。而父子兄弟朋友亲戚人生日用之懿伦。渐如既晦之月。但有黯然之魄而已者也。诚可为之举天下而相向而痛哭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