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x 页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书
书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2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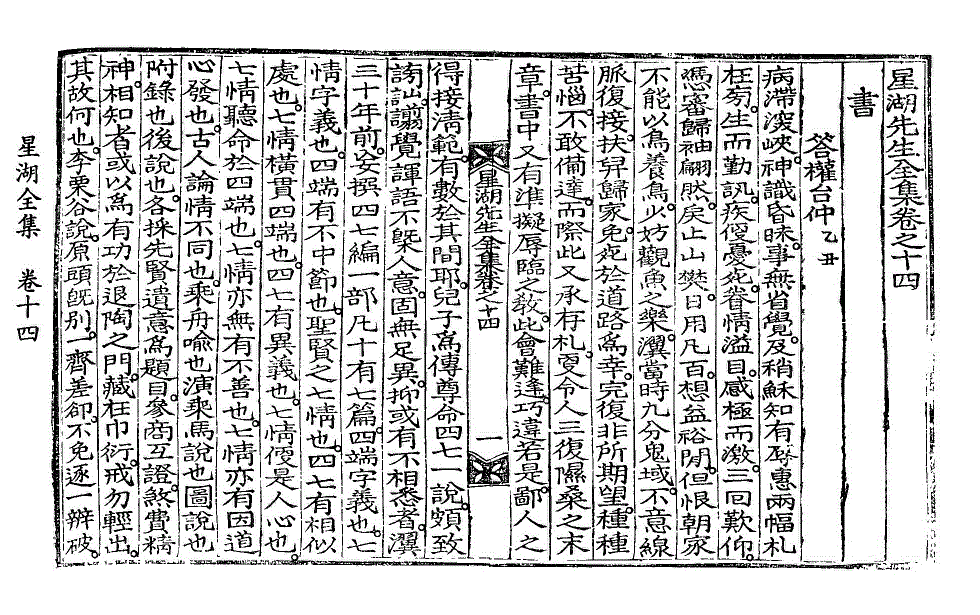 答权台仲(乙丑)
答权台仲(乙丑)病滞深峡。神识昏昧。事无省觉。及稍稣知有辱惠两幅札在旁。生而勤讯。疾便忧死。眷情溢目。感极而激。三回叹仰。凭审归袖翩然。戾止山樊。日用凡百。想益裕閒。但恨朝家不能以鸟养鸟。少妨观鱼之乐。瀷当时九分鬼域。不意线脉复接。扶舁归家。免死于道路为幸。完复非所期望。种种苦恼。不敢备达。而际此又承存札。更令人三复隰桑之末章。书中又有准拟辱临之教。此会难逢。巧违若是。鄙人之得接清范。有数于其间耶。儿子为传尊命四七一说。颇致谤讪。谫觉诨语不槩人意。固无足异。抑或有不相悉者。瀷三十年前。妄撰四七编一部凡十有七篇。四端字义也。七情字义也。四端有不中节也。圣贤之七情也。四七有相似处也。七情横贯四端也。四七有异义也。七情便是人心也。七情听命于四端也。七情亦无有不善也。七情亦有因道心发也。古人论情不同也。乘舟喻也演乘马说也图说也附录也后说也。各采先贤遗意为题目。参商互證。煞费精神。相知者或以为有功于退陶之门。藏在巾衍。戒勿轻出。其故何也。李栗谷说。原头既别。一齐差却。不免逐一辨破。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2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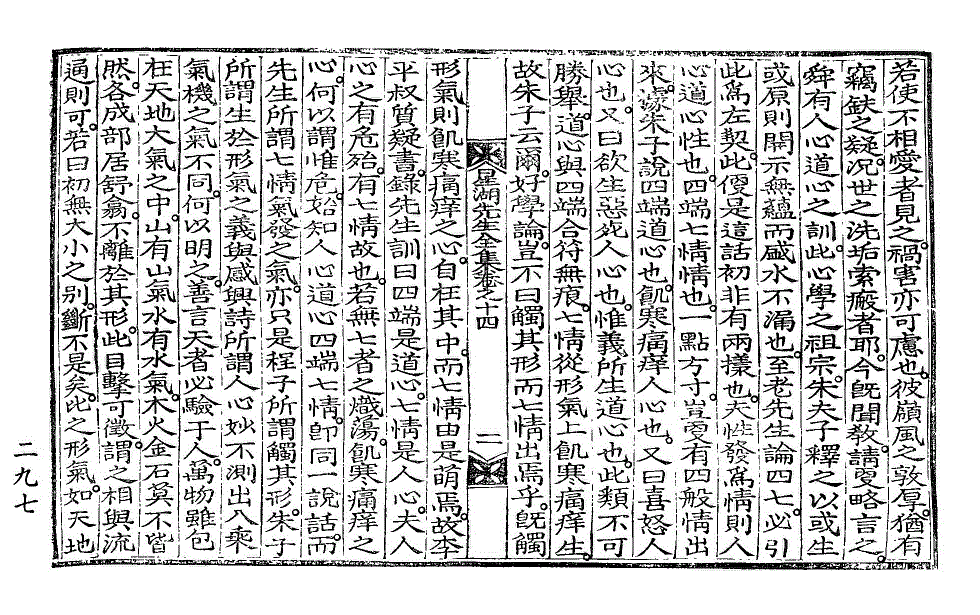 若使不相爱者见之。祸害亦可虑也。彼岭风之敦厚。犹有窃鈇之疑。况世之洗垢索瘢者耶。今既闻教。请更略言之。舜有人心道心之训。此心学之祖宗。朱夫子释之以或生或原则开示无蕴而盛水不漏也。至老先生论四七。必引此为左契。此便是这话初非有两㨾也。夫性发为情则人心道心性也。四端七情情也。一点方寸。岂更有四般情出来。据朱子说四端道心也。饥寒痛痒人心也。又曰喜怒人心也。又曰欲生恶死人心也。惟义所生道心也。此类不可胜举。道心与四端合符无痕。七情从形气上饥寒痛痒生。故朱子云尔。好学论。岂不曰触其形而七情出焉乎。既触形气则饥寒痛痒之心。自在其中。而七情由是萌焉。故李平叔质疑书。录先生训曰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夫人心之有危殆。有七情故也。若无七者之炽荡。饥寒痛痒之心。何以谓惟危。始知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即同一说话。而先生所谓七情气发之气。亦只是程子所谓触其形。朱子所谓生于形气之义与感兴诗所谓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之气不同。何以明之。善言天者必验于人。万物虽包在天地大气之中。山有山气水有水气。木火金石莫不皆然。各成部居舒翕。不离于其形。此目击可徵。谓之相与流通则可。若曰初无大小之别。断不是矣。比之形气。如天地
若使不相爱者见之。祸害亦可虑也。彼岭风之敦厚。犹有窃鈇之疑。况世之洗垢索瘢者耶。今既闻教。请更略言之。舜有人心道心之训。此心学之祖宗。朱夫子释之以或生或原则开示无蕴而盛水不漏也。至老先生论四七。必引此为左契。此便是这话初非有两㨾也。夫性发为情则人心道心性也。四端七情情也。一点方寸。岂更有四般情出来。据朱子说四端道心也。饥寒痛痒人心也。又曰喜怒人心也。又曰欲生恶死人心也。惟义所生道心也。此类不可胜举。道心与四端合符无痕。七情从形气上饥寒痛痒生。故朱子云尔。好学论。岂不曰触其形而七情出焉乎。既触形气则饥寒痛痒之心。自在其中。而七情由是萌焉。故李平叔质疑书。录先生训曰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夫人心之有危殆。有七情故也。若无七者之炽荡。饥寒痛痒之心。何以谓惟危。始知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即同一说话。而先生所谓七情气发之气。亦只是程子所谓触其形。朱子所谓生于形气之义与感兴诗所谓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之气不同。何以明之。善言天者必验于人。万物虽包在天地大气之中。山有山气水有水气。木火金石莫不皆然。各成部居舒翕。不离于其形。此目击可徵。谓之相与流通则可。若曰初无大小之别。断不是矣。比之形气。如天地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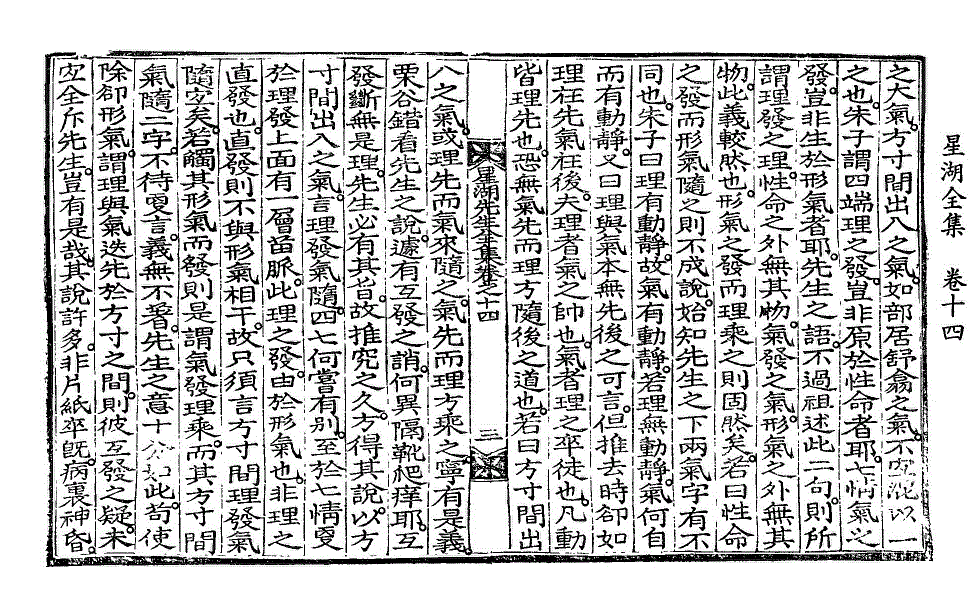 之大气。方寸间出入之气。如部居舒翕之气。不宜混以一之也。朱子谓四端理之发。岂非原于性命者耶。七情气之发。岂非生于形气者耶。先生之语。不过祖述此二句。则所谓理发之理。性命之外无其物。气发之气。形气之外无其物。此义较然也。形气之发而理乘之则固然矣。若曰性命之发而形气随之则不成说。始知先生之下两气字有不同也。朱子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又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夫理者气之帅也。气者理之卒徒也。凡动皆理先也。恐无气先而理方随后之道也。若曰方寸间出入之气。或理先而气来随之。气先而理方乘之。宁有是义。栗谷错看先生之说。遽有互发之诮。何异隔靴爬痒耶。互发断无是理。先生必有其旨。故推究之久。方得其说。以方寸间出入之气。言理发气随。四七何尝有别。至于七情更于理发上面有一层苗脉。此理之发。由于形气也。非理之直发也。直发则不与形气相干。故只须言方寸间理发气随宜矣。若触其形气而发则是谓气发理乘。而其方寸间气随二字。不待更言。义无不著。先生之意十分如此。苟使除却形气。谓理与气迭先于方寸之间。则彼互发之疑。未宜全斥先生。岂有是哉。其说许多。非片纸卒既。病里神昏。
之大气。方寸间出入之气。如部居舒翕之气。不宜混以一之也。朱子谓四端理之发。岂非原于性命者耶。七情气之发。岂非生于形气者耶。先生之语。不过祖述此二句。则所谓理发之理。性命之外无其物。气发之气。形气之外无其物。此义较然也。形气之发而理乘之则固然矣。若曰性命之发而形气随之则不成说。始知先生之下两气字有不同也。朱子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又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夫理者气之帅也。气者理之卒徒也。凡动皆理先也。恐无气先而理方随后之道也。若曰方寸间出入之气。或理先而气来随之。气先而理方乘之。宁有是义。栗谷错看先生之说。遽有互发之诮。何异隔靴爬痒耶。互发断无是理。先生必有其旨。故推究之久。方得其说。以方寸间出入之气。言理发气随。四七何尝有别。至于七情更于理发上面有一层苗脉。此理之发。由于形气也。非理之直发也。直发则不与形气相干。故只须言方寸间理发气随宜矣。若触其形气而发则是谓气发理乘。而其方寸间气随二字。不待更言。义无不著。先生之意十分如此。苟使除却形气。谓理与气迭先于方寸之间。则彼互发之疑。未宜全斥先生。岂有是哉。其说许多。非片纸卒既。病里神昏。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298L 页
 亦何能该举。栗谷说其大旨不出于四端是七情中善一边。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与鄙意一霄一壤彼东此西。谓之相涉者过矣。惟舜怒孟喜一段。高峰后说终守理发之义。而先生亟许。瀷初说断作气发。然每以先生为重。故后复委曲为说。勉循高峰。而此中朋友有限界不明之疑。瀷亦不敢自是。以待更加评订。非我也高峰也。而先生许之者也。瀷特不自信而信古人也。变旧之疑。或者因此起耶。未可知也。畴昔之日。瀷就遗集中采可师可法者。分门类汇。为道东录一册。又采言礼者。各取其要旨为题目。自冠昏至乡邦之礼。次第编入。为李先生礼说上下册。后来诸儒之发挥者。无不集录。读是书者取之。恐不为无助。但恨乏纸札。犹未及净写耳。病馀神气毁剥。眼乱手掉。语没伦脊。字不成㨾。惫倦而止此。山川阻脩。未死之前。无缘奉袂。承教怅怀难胜。惟愿益懋尊德。庸副区区远诚。
亦何能该举。栗谷说其大旨不出于四端是七情中善一边。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与鄙意一霄一壤彼东此西。谓之相涉者过矣。惟舜怒孟喜一段。高峰后说终守理发之义。而先生亟许。瀷初说断作气发。然每以先生为重。故后复委曲为说。勉循高峰。而此中朋友有限界不明之疑。瀷亦不敢自是。以待更加评订。非我也高峰也。而先生许之者也。瀷特不自信而信古人也。变旧之疑。或者因此起耶。未可知也。畴昔之日。瀷就遗集中采可师可法者。分门类汇。为道东录一册。又采言礼者。各取其要旨为题目。自冠昏至乡邦之礼。次第编入。为李先生礼说上下册。后来诸儒之发挥者。无不集录。读是书者取之。恐不为无助。但恨乏纸札。犹未及净写耳。病馀神气毁剥。眼乱手掉。语没伦脊。字不成㨾。惫倦而止此。山川阻脩。未死之前。无缘奉袂。承教怅怀难胜。惟愿益懋尊德。庸副区区远诚。答权台仲(丁卯)
翳翳颓景。落落音信。盍簪非所论也。宁不怅然。向者因京便。忽漫承拜下状。虽非近缄。亦既凭慰。又不审凉节。特地清閒。趣适味佳。益有山水之乐耶。多令人缅怀。瀷衰疾弥增。丧威遝至。同气四室。鳏翁兀留。只得以理宽之耳。近又稍理旧学。时观易一二卦。益知向来之草草。然精魂毁剥。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2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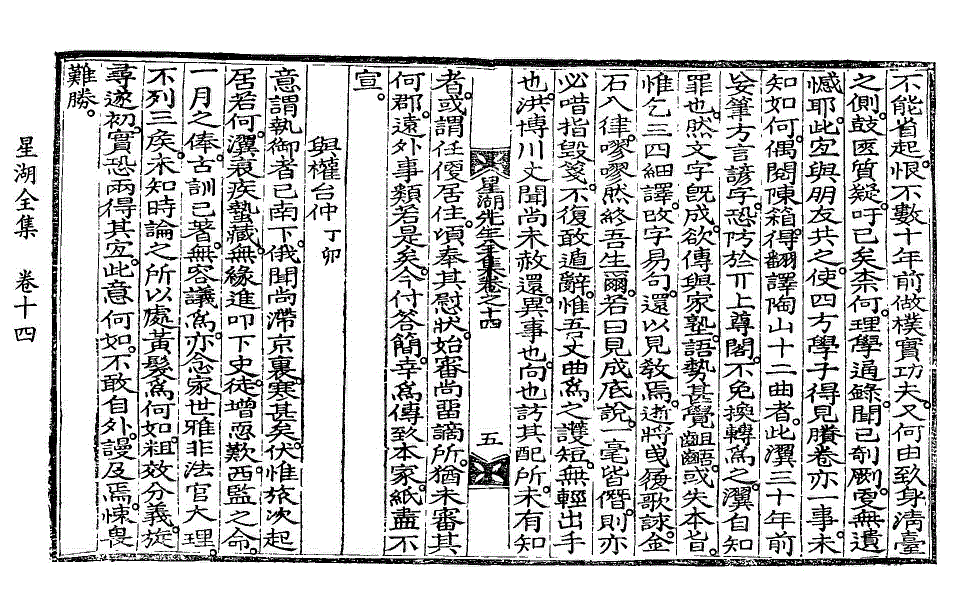 不能省起。恨不数十年前做朴实功夫。又何由致身清台之侧。鼓箧质疑。吁已矣柰何。理学通录。闻已剞劂。更无遗憾耶。此宜与朋友共之。使四方学子得见剩卷亦一事。未知如何。偶阅陈箱。得翻译陶山十二曲者。此瀷三十年前妄笔方言谚字。恐防于丌上尊阁。不免换转为之。瀷自知罪也。然文字既成。欲传与家塾。语势甚觉龃龉。或失本旨。惟乞三四细译。改字易句。还以见教焉。逝将曳履歌咏。金石八律。嘐嘐然终吾生尔。若曰见成底说。一毫皆僭。则亦必唶指毁笺。不复敢遁辞。惟吾丈曲为之护短。无轻出手也。洪博川丈闻尚未赦还。异事也。向也访其配所。未有知者。或谓任便居住。顷奉其慰状。始审尚留谪所。犹未审其何郡。远外事类若是矣。今付答简。幸为传致本家。纸尽不宣。
不能省起。恨不数十年前做朴实功夫。又何由致身清台之侧。鼓箧质疑。吁已矣柰何。理学通录。闻已剞劂。更无遗憾耶。此宜与朋友共之。使四方学子得见剩卷亦一事。未知如何。偶阅陈箱。得翻译陶山十二曲者。此瀷三十年前妄笔方言谚字。恐防于丌上尊阁。不免换转为之。瀷自知罪也。然文字既成。欲传与家塾。语势甚觉龃龉。或失本旨。惟乞三四细译。改字易句。还以见教焉。逝将曳履歌咏。金石八律。嘐嘐然终吾生尔。若曰见成底说。一毫皆僭。则亦必唶指毁笺。不复敢遁辞。惟吾丈曲为之护短。无轻出手也。洪博川丈闻尚未赦还。异事也。向也访其配所。未有知者。或谓任便居住。顷奉其慰状。始审尚留谪所。犹未审其何郡。远外事类若是矣。今付答简。幸为传致本家。纸尽不宣。与权台仲(丁卯)
意谓执御者已南下。俄闻尚滞京里。寒甚矣。伏惟旅次起居若何。瀷衰疾蛰藏。无缘进叩下史。徒增恧叹。西监之命。一月之俸。古训已著。无容议为。亦念家世雅非法官大理。不列三侯。未知时论之所以处黄发为何如。粗效分义。旋寻遂初。实恐两得其宜。此意何如。不敢自外。谩及焉。悚畏难胜。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2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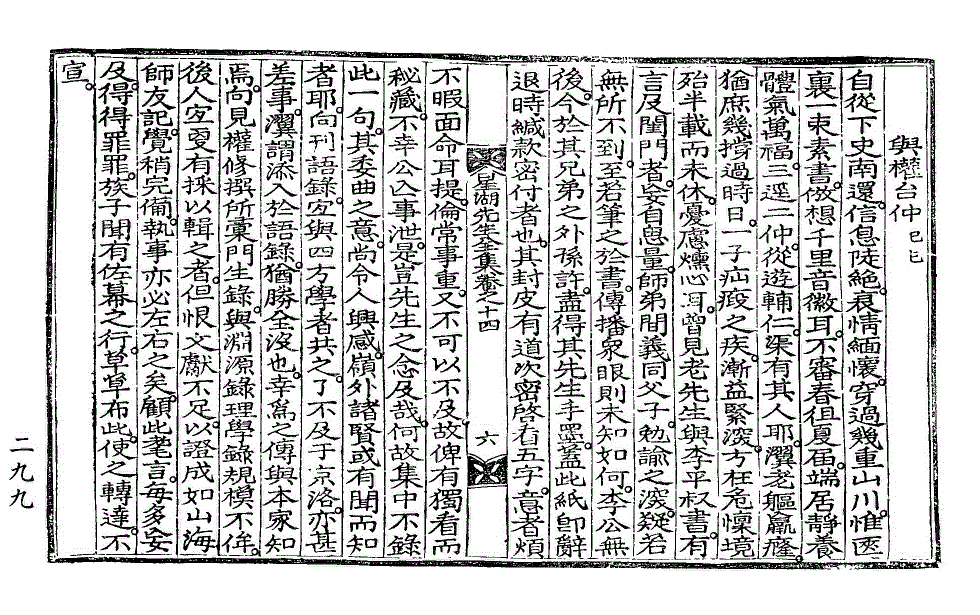 与权台仲(己巳)
与权台仲(己巳)自从下史南还。信息陡绝。衰情缅怀。穿过几重山川。惟箧里一束素书。仿想千里音徽耳。不审春徂夏届。端居静养体气万福。三径二仲。从游辅仁。渠有其人耶。瀷老躯羸癃。犹庶几撑过时日。一子疝瘕之疾。渐益紧深。方在危懔境殆半载而未休。忧虑熏心耳。曾见老先生与李平叔书。有言及闺门者。妄自思量。师弟间义同父子。勉谕之深。疑若无所不到。至若笔之于书。传播众眼则未知如何。李公无后。今于其兄弟之外孙许。尽得其先生手墨。盖此纸即辞退时缄款密付者也。其封皮有道次密启看五字。意者烦不暇面命耳提。伦常事重。又不可以不及。故俾有独看而秘藏。不幸公亡事泄。是岂先生之念及哉。何故集中不录此一句。其委曲之意。尚令人兴感。岭外诸贤或有闻而知者耶。向刊语录。宜与四方学者共之。了不及于京洛。亦甚差事。瀷谓添入于语录。犹胜全没也。幸为之传与本家知焉。向见权修撰所汇门生录。与渊源录理学录规模不侔。后人宜更有采以辑之者。但恨文献不足。以證成如山海师友记。觉稍完备。执事亦必左右之矣。顾此耄言。每多妄及。得得罪罪。族子闻有佐幕之行。草草布此。使之转达。不宣。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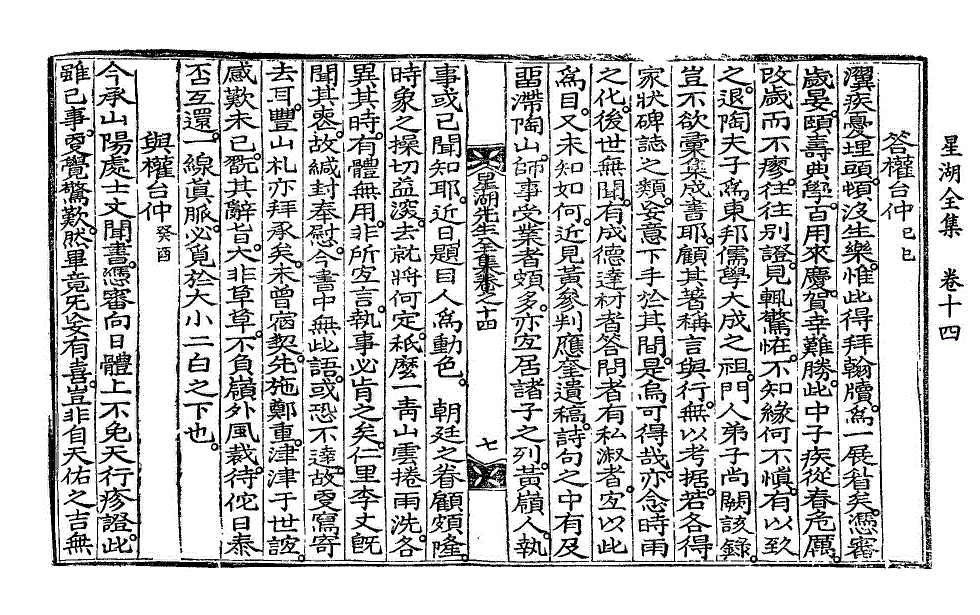 答权台仲(己巳)
答权台仲(己巳)瀷疾忧埋头。顿没生乐。惟此得拜翰牍。为一展眉矣。凭审岁晏。颐寿典学。百用来庆。贺幸难胜。此中子疾从春危厉。改岁而不瘳。往往别證。见辄惊怪。不知缘何不慎。有以致之。退陶夫子为东邦儒学大成之祖。门人弟子尚阙该录。岂不欲汇集成书耶。顾其著称言与行。无以考据。若各得家状碑志之类。妄意下手于其间。是乌可得哉。亦念时雨之化。后世无闻。有成德达材者答问者有私淑者。宜以此为目。又未知如何。近见黄参判应奎遗稿。诗句之中有及留滞陶山。师事受业者颇多。亦宜居诸子之列。黄岭人。执事或已闻知耶。近日题目人为动色。 朝廷之眷顾颇隆。时象之操切益深。去就将何定。秖么一青山云捲雨洗。各异其时。有体无用。非所宜言。执事必肯之矣。仁里李丈既闻其丧。故缄封奉慰。今书中无此语。或恐不达。故更写寄去耳。丰山札亦拜承矣。未曾宿契。先施郑重。津津于世谊。感叹未已。玩其辞旨。大非草草。不负岭外风裁。待佗日泰否互还。一线真脉。必觅于大小二白之下也。
与权台仲(癸酉)
今承山阳处士丈闻书。凭审向日体上不免天行疹證。此虽已事。更觉惊叹。然毕竟无妄有喜。岂非自天佑之吉无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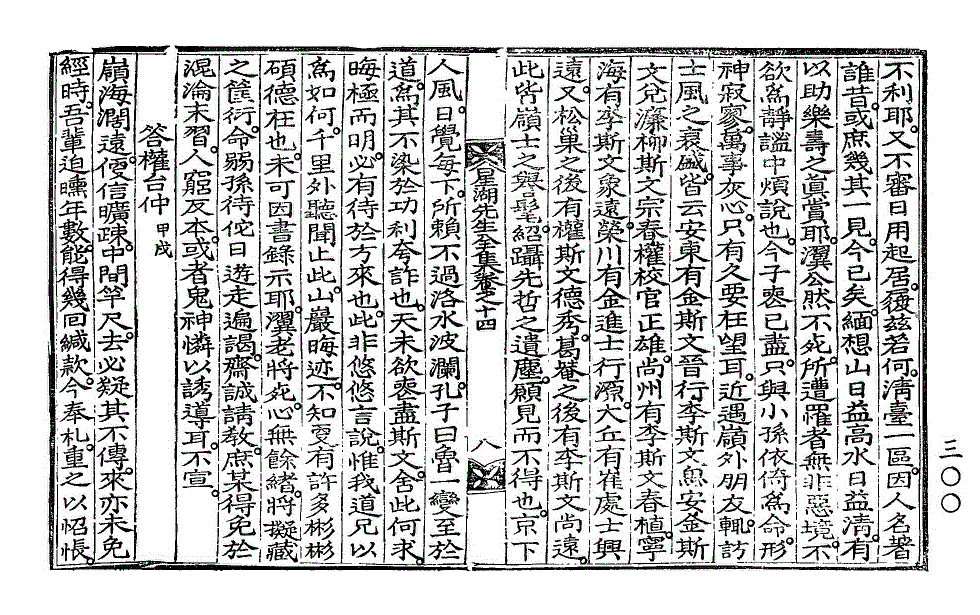 不利耶。又不审日用起居。履玆若何。清台一区。因人名著谁昔。或庶几其一见。今已矣。缅想山日益高水日益清。有以助乐寿之真赏耶。瀷公然不死。所遭罹者无非恶境。不欲为静谧中烦说也。今子丧已尽。只与小孙依倚为命。形神寂寥。万事灰心。只有久要在望耳。近遇岭外朋友。辄访士风之衰盛。皆云安东有金斯文晋行,李斯文思安,金斯文兑濂,柳斯文宗春,权校官正雄。尚州有李斯文春植。宁海有李斯文象远。荣川有金进士行源。大丘有崔处士兴远。又松巢之后有权斯文德秀。葛庵之后有李斯文尚远。此皆岭士之誉髦。绍蹑先哲之遗尘。愿见而不得也。京下人风。日觉每下。所赖不过洛水波澜。孔子曰鲁一变至于道。为其不染于功利夸诈也。天未欲丧尽斯文。舍此何求。晦极而明。必有待于方来也。此非悠悠言说。惟我道兄以为如何。千里外听闻止此。山岩晦迹。不知更有许多彬彬硕德在也。未可因书录示耶。瀷老将死。心无馀绪。将拟藏之筐衍。命弱孙待佗日游走遍谒。斋诚请教。庶某得免于混沦末习。人穷反本。或者鬼神怜以诱导耳。不宣。
不利耶。又不审日用起居。履玆若何。清台一区。因人名著谁昔。或庶几其一见。今已矣。缅想山日益高水日益清。有以助乐寿之真赏耶。瀷公然不死。所遭罹者无非恶境。不欲为静谧中烦说也。今子丧已尽。只与小孙依倚为命。形神寂寥。万事灰心。只有久要在望耳。近遇岭外朋友。辄访士风之衰盛。皆云安东有金斯文晋行,李斯文思安,金斯文兑濂,柳斯文宗春,权校官正雄。尚州有李斯文春植。宁海有李斯文象远。荣川有金进士行源。大丘有崔处士兴远。又松巢之后有权斯文德秀。葛庵之后有李斯文尚远。此皆岭士之誉髦。绍蹑先哲之遗尘。愿见而不得也。京下人风。日觉每下。所赖不过洛水波澜。孔子曰鲁一变至于道。为其不染于功利夸诈也。天未欲丧尽斯文。舍此何求。晦极而明。必有待于方来也。此非悠悠言说。惟我道兄以为如何。千里外听闻止此。山岩晦迹。不知更有许多彬彬硕德在也。未可因书录示耶。瀷老将死。心无馀绪。将拟藏之筐衍。命弱孙待佗日游走遍谒。斋诚请教。庶某得免于混沦末习。人穷反本。或者鬼神怜以诱导耳。不宣。答权台仲(甲戌)
岭海阔远。便信旷疏。中间竿尺。去必疑其不传。来亦未免经时。吾辈迫曛年数。能得几回缄款。今奉札。重之以怊怅。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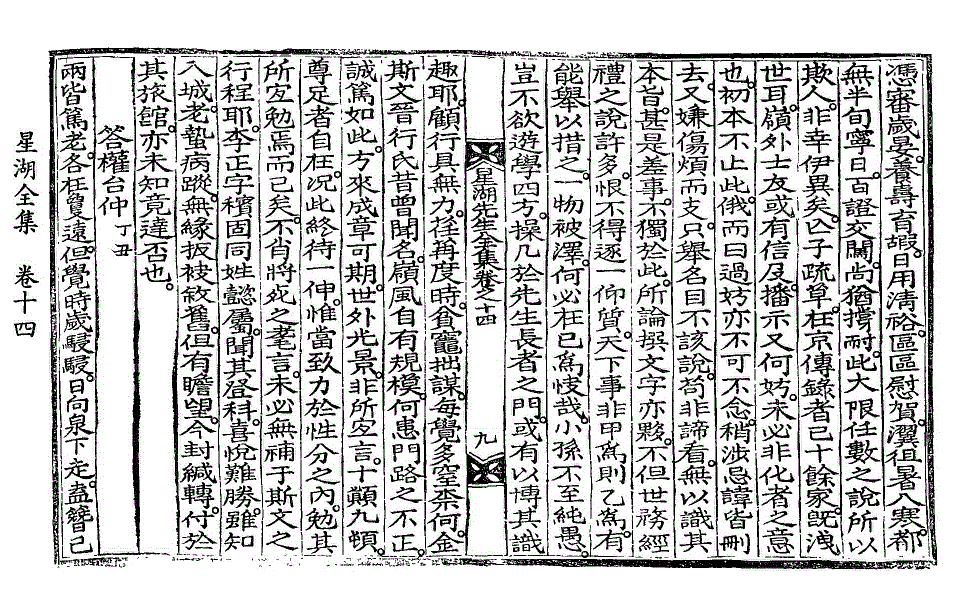 凭审岁晏。养寿育嘏。日用清裕。区区慰贺。瀷徂暑入寒。都无半旬宁日。百證交闯。尚犹撑耐。此大限任数之说所以欺人。非幸伊异矣。亡子疏草。在京传录者已十馀家。既泄世耳。岭外士友或有信及。播示又何妨。未必非化者之意也。初本不止此。俄而曰过妨亦不可不念。稍涉忌讳皆删去。又嫌伤烦而支。只举名目不该说。苟非谛看。无以识其本旨。甚是差事。不独于此。所论撰文字亦夥。不但世务经礼之说许多。恨不得逐一仰质。天下事非甲为则乙为。有能举以措之。一物被泽。何必在己为快哉。小孙不至纯愚。岂不欲游学四方。操几于先生长者之门。或有以博其识趣耶。顾行具无力。荏苒度时。贫灶拙谋。每觉多窒柰何。金斯文晋行氏昔曾闻名。岭风自有规模。何患门路之不正。诚笃如此。方来成章可期。世外光景。非所宜言。十颠九顿。尊足者自在。况此终待一伸。惟当致力于性分之内。勉其所宜勉焉而已矣。不肖将死之耄言。未必无补于斯文之行程耶。李正字穦固同姓懿属。闻其登科。喜悦难胜。虽知入城。老蛰病踪。无缘扳袂叙旧。但有瞻望。今封缄转。付于其旅馆。亦未知竟达否也。
凭审岁晏。养寿育嘏。日用清裕。区区慰贺。瀷徂暑入寒。都无半旬宁日。百證交闯。尚犹撑耐。此大限任数之说所以欺人。非幸伊异矣。亡子疏草。在京传录者已十馀家。既泄世耳。岭外士友或有信及。播示又何妨。未必非化者之意也。初本不止此。俄而曰过妨亦不可不念。稍涉忌讳皆删去。又嫌伤烦而支。只举名目不该说。苟非谛看。无以识其本旨。甚是差事。不独于此。所论撰文字亦夥。不但世务经礼之说许多。恨不得逐一仰质。天下事非甲为则乙为。有能举以措之。一物被泽。何必在己为快哉。小孙不至纯愚。岂不欲游学四方。操几于先生长者之门。或有以博其识趣耶。顾行具无力。荏苒度时。贫灶拙谋。每觉多窒柰何。金斯文晋行氏昔曾闻名。岭风自有规模。何患门路之不正。诚笃如此。方来成章可期。世外光景。非所宜言。十颠九顿。尊足者自在。况此终待一伸。惟当致力于性分之内。勉其所宜勉焉而已矣。不肖将死之耄言。未必无补于斯文之行程耶。李正字穦固同姓懿属。闻其登科。喜悦难胜。虽知入城。老蛰病踪。无缘扳袂叙旧。但有瞻望。今封缄转。付于其旅馆。亦未知竟达否也。答权台仲(丁丑)
两皆笃老。各在夐远。但觉时岁骎骎。日向泉下走。盍簪已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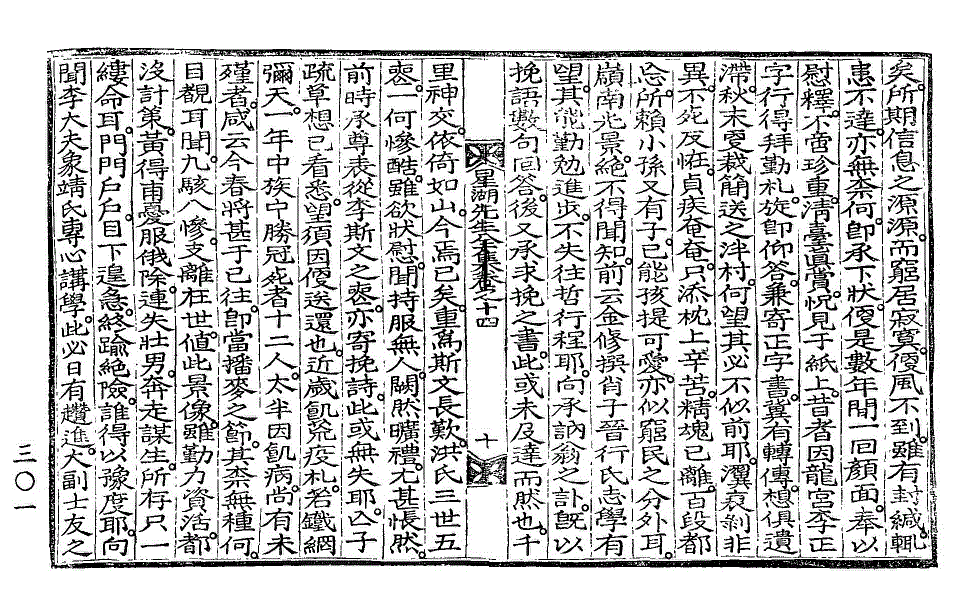 矣。所期信息之源源。而穷居寂寞。便风不到。虽有封缄。辄患不达。亦无柰何。即承下状。便是数年间一回颜面。奉以慰释。不啻珍重。清台真赏。恍见于纸上。昔者因龙宫李正字行得拜勤札。旋即仰答。兼寄正字书。冀有转传。想俱遗滞。秋末更裁简送之泮村。何望其必不似前耶。瀷衰剥非异。不死反怪。贞疾奄奄。只添枕上辛苦。精魂已离。百段都忘。所赖小孙又有子。已能孩提可爱。亦似穷民之分外耳。岭南光景。绝不得闻知。前云金修撰肖子晋行氏志学有望。其能勤勉进步。不失往哲行程耶。向承讷翁之讣。既以挽语数句回答。后又承求挽之书。此或未及达而然也。千里神交。依倚如山。今焉已矣。重为斯文长叹。洪氏三世五丧。一何惨酷。虽欲状慰。闻持服无人。阙然旷礼。尤甚怅然。前时承尊表从李斯文之丧。亦寄挽诗。此或无失耶。亡子疏草想已看悉。望须因便送还也。近岁饥荒疫札。若铁网弥天。一年中族中胜冠死者十二人。太半因饥病。尚有未殣者。咸云今春将甚于已往。即当播麦之节。其柰无种何。目睹耳闻。九骇八惨。支离在世。值此景像。虽勤力资活。都没计策。黄得甫忧服俄除。连失壮男。奔走谋生。所存只一缕命耳。门门户户。目下遑急。终踰绝险。谁得以豫度耶。向闻李大夫象靖氏专心讲学。此必日有趱进。大副士友之
矣。所期信息之源源。而穷居寂寞。便风不到。虽有封缄。辄患不达。亦无柰何。即承下状。便是数年间一回颜面。奉以慰释。不啻珍重。清台真赏。恍见于纸上。昔者因龙宫李正字行得拜勤札。旋即仰答。兼寄正字书。冀有转传。想俱遗滞。秋末更裁简送之泮村。何望其必不似前耶。瀷衰剥非异。不死反怪。贞疾奄奄。只添枕上辛苦。精魂已离。百段都忘。所赖小孙又有子。已能孩提可爱。亦似穷民之分外耳。岭南光景。绝不得闻知。前云金修撰肖子晋行氏志学有望。其能勤勉进步。不失往哲行程耶。向承讷翁之讣。既以挽语数句回答。后又承求挽之书。此或未及达而然也。千里神交。依倚如山。今焉已矣。重为斯文长叹。洪氏三世五丧。一何惨酷。虽欲状慰。闻持服无人。阙然旷礼。尤甚怅然。前时承尊表从李斯文之丧。亦寄挽诗。此或无失耶。亡子疏草想已看悉。望须因便送还也。近岁饥荒疫札。若铁网弥天。一年中族中胜冠死者十二人。太半因饥病。尚有未殣者。咸云今春将甚于已往。即当播麦之节。其柰无种何。目睹耳闻。九骇八惨。支离在世。值此景像。虽勤力资活。都没计策。黄得甫忧服俄除。连失壮男。奔走谋生。所存只一缕命耳。门门户户。目下遑急。终踰绝险。谁得以豫度耶。向闻李大夫象靖氏专心讲学。此必日有趱进。大副士友之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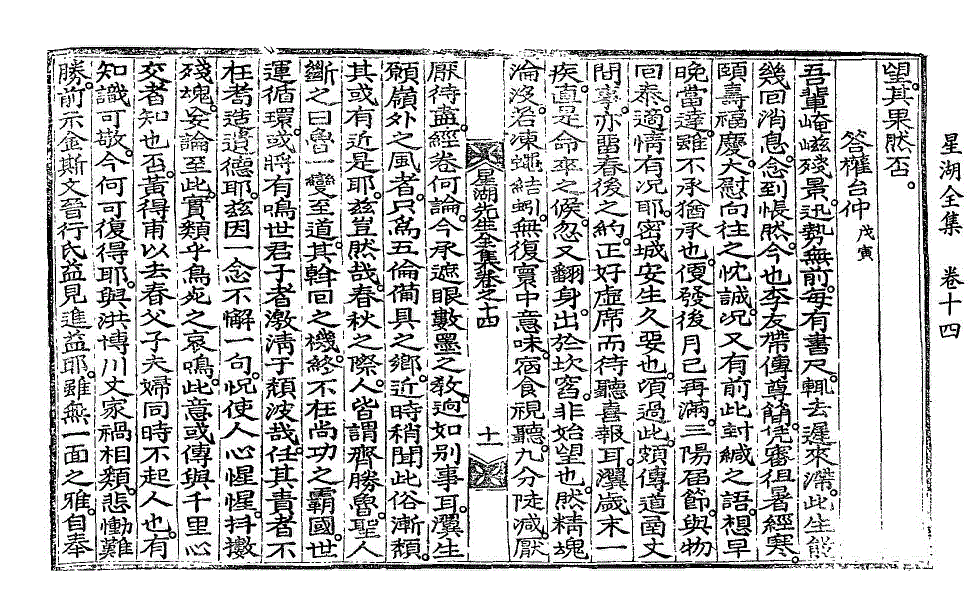 望。其果然否。
望。其果然否。答权台仲(戊寅)
吾辈崦嵫残景。迅势无前。每有书尺。辄去迟来滞。此生能几回消息。念到怅然。今也李友带传尊简。凭审徂暑经寒。颐寿福庆。大慰向往之忱诚。况又有前此封缄之语。想早晚当达。虽不承犹承也。便发后月已再满。三阳届节。与物回泰。适情有况耶。密城安生久要也。顷过此。颇传道函丈间事。亦留春后之约。正好虚席而待听喜报耳。瀷岁末一疾。直是命卒之候。忽又翻身。出于坎窞。非始望也。然精魂沦没。若冻蝇结蚓。无复寰中意味。宿食视听。九分陡减。厌厌待尽。经卷何论。今承遮眼数墨之教。迥如别事耳。瀷生愿岭外之风者。只为五伦备具之乡。近时稍闻此俗渐颓。其或有近是耶。玆岂然哉。春秋之际。人皆谓齐胜鲁。圣人断之曰鲁一变至道。其斡回之机。终不在尚功之霸国。世运循环。或将有鸣世君子者激清于颓波哉。任其责者不在耇造遗德耶。玆因一念不懈一句。恍使人心惺惺。抖擞残魂。妄论至此。实类乎鸟死之哀鸣。此意或传与千里心交者知也否。黄得甫以去春父子夫妇同时不起人也。有知识可敬。今何可复得耶。与洪博川丈家祸相类。悲恸难胜。前示金斯文晋行氏益见进益耶。虽无一面之雅。自奉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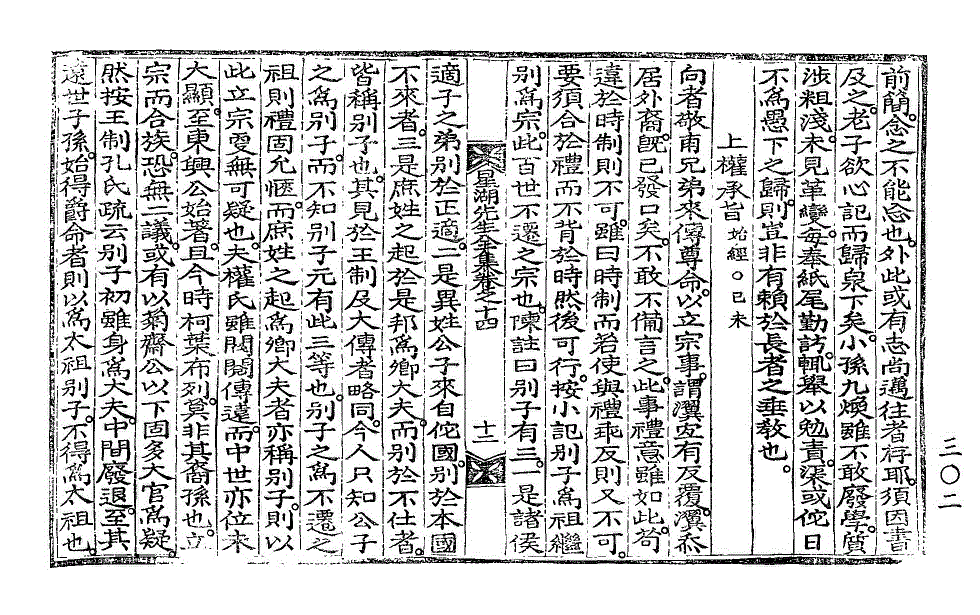 前简。念之不能忘也。外此或有志尚迈往者存耶。须因书及之。老子欲心记而归泉下矣。小孙九焕虽不敢废学。质涉粗浅。未见革变。每奉纸尾勤访。辄举以勉责。渠或佗日不为愚下之归。则岂非有赖于长者之垂教也。
前简。念之不能忘也。外此或有志尚迈往者存耶。须因书及之。老子欲心记而归泉下矣。小孙九焕虽不敢废学。质涉粗浅。未见革变。每奉纸尾勤访。辄举以勉责。渠或佗日不为愚下之归。则岂非有赖于长者之垂教也。上权承旨(始经○己未)
向者敬甫兄弟来传尊命。以立宗事。谓瀷宜有反覆。瀷忝居外裔。既已发口矣。不敢不备言之。此事礼意虽如此。苟违于时制则不可。虽曰时制而若使与礼乖反则又不可。要须合于礼而不背于时然后可行。按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此百世不迁之宗也。陈注曰别子有三。一是诸侯适子之弟别于正适。二是异姓公子来自佗国。别于本国不来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为卿大夫。而别于不仕者。皆称别子也。其见于王制及大传者略同。今人只知公子之为别子。而不知别子元有此三等也。别子之为不迁之祖则礼固允惬。而庶姓之起为卿大夫者亦称别子。则以此立宗更无可疑也。夫权氏虽阀阅传远。而中世亦位未大显。至东兴公始著。且今时柯叶布列。莫非其裔孙也。立宗而合族。恐无二议。或有以菊斋公以下固多大官为疑。然按王制孔氏疏云别子初虽身为大夫。中间废退。至其远世子孙。始得爵命者则以为太祖别子。不得为太祖也。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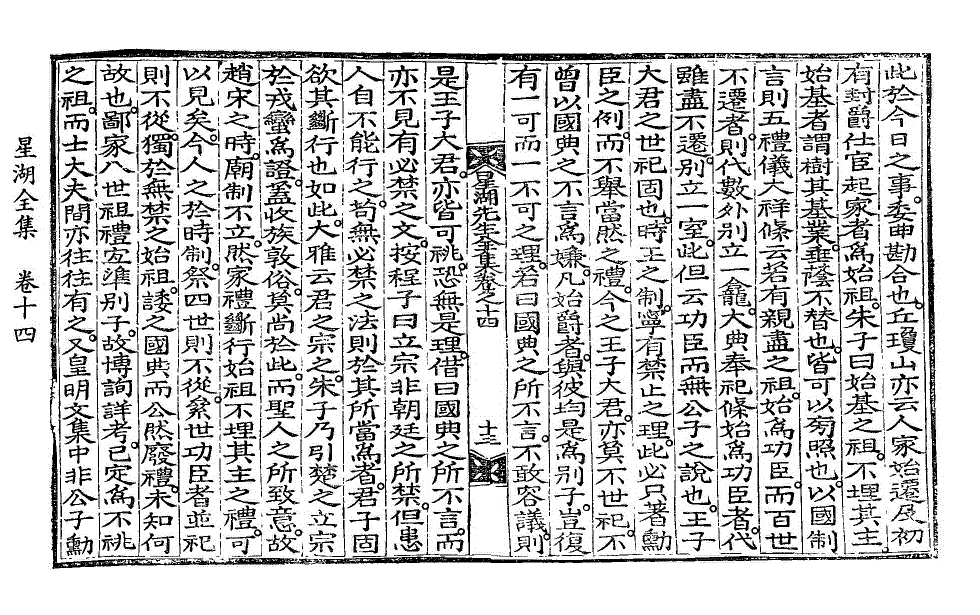 此于今日之事。委曲勘合也。丘琼山亦云人家始迁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为始祖。朱子曰始基之祖。不埋其主。始基者谓树其基业。垂荫不替也。皆可以旁照也。以国制言则五礼仪大祥条云若有亲尽之祖。始为功臣。而百世不迁者。则代数外别立一龛。大典奉祀条始为功臣者。代虽尽不迁。别立一室。此但云功臣而无公子之说也。王子大君之世祀固也。时王之制。宁有禁止之理。此必只著勋臣之例。而不举当然之礼。今之王子大君。亦莫不世祀。不曾以国典之不言为嫌。凡始爵者。与彼均是为别子。岂复有一可而一不可之理。若曰国典之所不言。不敢容议。则是王子大君。亦皆可祧。恐无是理。借曰国典之所不言。而亦不见有必禁之文。按程子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苟无必禁之法则于其所当为者。君子固欲其断行也如此。大雅云君之宗之。朱子乃引楚之立宗于戎蛮为證。盖收族敦俗。莫尚于此。而圣人之所致意。故赵宋之时。庙制不立。然家礼断行始祖不埋其主之礼。可以见矣。今人之于时制。祭四世则不从。累世功臣者并祀则不从。独于无禁之始祖。诿之国典而公然废礼。未知何故也。鄙家八世祖礼宜准别子。故博询详考。已定为不祧之祖。而士大夫间亦往往有之。又皇明文集中非公子勋
此于今日之事。委曲勘合也。丘琼山亦云人家始迁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为始祖。朱子曰始基之祖。不埋其主。始基者谓树其基业。垂荫不替也。皆可以旁照也。以国制言则五礼仪大祥条云若有亲尽之祖。始为功臣。而百世不迁者。则代数外别立一龛。大典奉祀条始为功臣者。代虽尽不迁。别立一室。此但云功臣而无公子之说也。王子大君之世祀固也。时王之制。宁有禁止之理。此必只著勋臣之例。而不举当然之礼。今之王子大君。亦莫不世祀。不曾以国典之不言为嫌。凡始爵者。与彼均是为别子。岂复有一可而一不可之理。若曰国典之所不言。不敢容议。则是王子大君。亦皆可祧。恐无是理。借曰国典之所不言。而亦不见有必禁之文。按程子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苟无必禁之法则于其所当为者。君子固欲其断行也如此。大雅云君之宗之。朱子乃引楚之立宗于戎蛮为證。盖收族敦俗。莫尚于此。而圣人之所致意。故赵宋之时。庙制不立。然家礼断行始祖不埋其主之礼。可以见矣。今人之于时制。祭四世则不从。累世功臣者并祀则不从。独于无禁之始祖。诿之国典而公然废礼。未知何故也。鄙家八世祖礼宜准别子。故博询详考。已定为不祧之祖。而士大夫间亦往往有之。又皇明文集中非公子勋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3L 页
 臣而立庙世祀者极多。皆可考以知也。或又曰非国家之所命而取舍于祖先未安。此又不审祖有功宗有德。故有国者亦然。殷有两宗。周之追王。只及三世。宋祖懿祖。莫非取舍于其先。彼天子谁所命也。苟有功德于子孙者则贤其贤而亲其亲。世数虽远。于戏不忘。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免也。鄙见如此。伏望商量去就。
臣而立庙世祀者极多。皆可考以知也。或又曰非国家之所命而取舍于祖先未安。此又不审祖有功宗有德。故有国者亦然。殷有两宗。周之追王。只及三世。宋祖懿祖。莫非取舍于其先。彼天子谁所命也。苟有功德于子孙者则贤其贤而亲其亲。世数虽远。于戏不忘。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免也。鄙见如此。伏望商量去就。答权进士(信经○甲辰)
过询先夫人再期。虽厌降丧毕。而心制犹存。况今几筵未撤。馈食犹奉。则与佗忌日尤有所不同者。 国恤成服之后何可昧然不行乎。瀷意则虽寻常忌日。无不可行之义。儒贤已有言者矣。退溪答李刚而书云以素馔行事。此则可疑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事死而素馔。不见考据。况成服之后。鲜羽之属。市肆如故。是许民食之也。独不可以此祭先耶。西厓答郑子精书亦云略设素馔。金鹤沙四礼问答中此条之下。添注云非谓全不用鱼肉。夫厓老亲承于退门。鹤沙又出厓门。而其说如此。恐或有可以商量处。但合有丰杀之节耳。至于墓祀。退溪答李刚而,郑道可,金而精书。皆云不上冢。就斋舍或庙中。如节祀行之。此又可疑。不可行则不行而已。以墓事而就庙中。似涉苟艰。且东俗四节上冢。如中国节祀之例。皆以生人宴乐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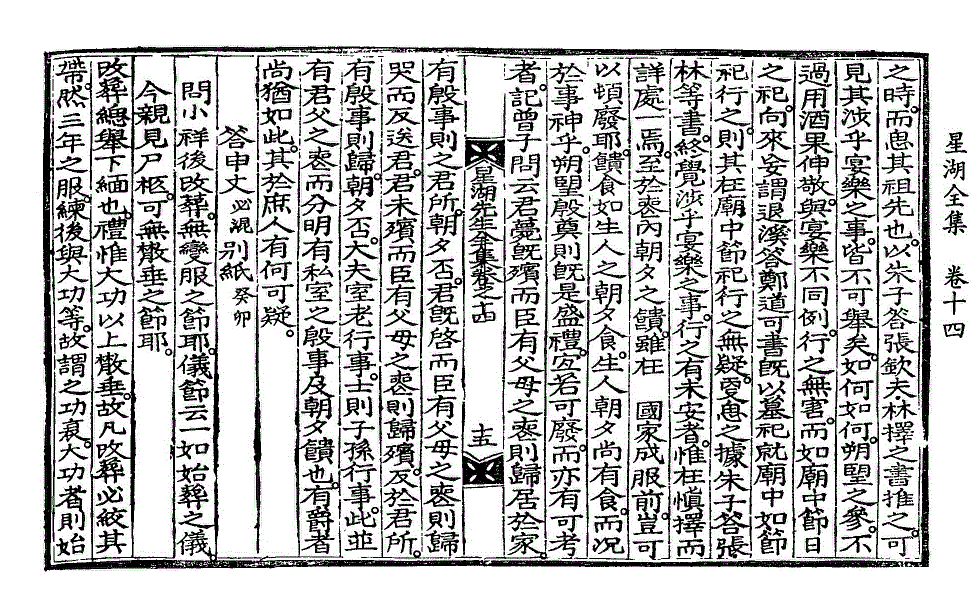 之时。而思其祖先也。以朱子答张钦夫,林择之书推之。可见其涉乎宴乐之事。皆不可举矣。如何如何。朔望之参。不过用酒果伸敬。与宴乐不同例。行之无害。而如庙中节日之祀。向来妄谓退溪答郑道可书既以墓祀就庙中如节祀行之。则其在庙中节祀行之无疑。更思之据朱子答张,林等书。终觉涉乎宴乐之事。行之有未安者。惟在慎择而详处一焉。至于丧内朝夕之馈。虽在 国家成服前。岂可以顿废耶。馈食如生人之朝夕食。生人朝夕尚有食。而况于事神乎。朔望殷奠则既是盛礼。宜若可废。而亦有可考者。记曾子问云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君既启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归哭而反送君。君未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则子孙行事。此并有君父之丧而分明有私室之殷事及朝夕馈也。有爵者尚犹如此。其于庶人有何可疑。
之时。而思其祖先也。以朱子答张钦夫,林择之书推之。可见其涉乎宴乐之事。皆不可举矣。如何如何。朔望之参。不过用酒果伸敬。与宴乐不同例。行之无害。而如庙中节日之祀。向来妄谓退溪答郑道可书既以墓祀就庙中如节祀行之。则其在庙中节祀行之无疑。更思之据朱子答张,林等书。终觉涉乎宴乐之事。行之有未安者。惟在慎择而详处一焉。至于丧内朝夕之馈。虽在 国家成服前。岂可以顿废耶。馈食如生人之朝夕食。生人朝夕尚有食。而况于事神乎。朔望殷奠则既是盛礼。宜若可废。而亦有可考者。记曾子问云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君既启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归哭而反送君。君未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则子孙行事。此并有君父之丧而分明有私室之殷事及朝夕馈也。有爵者尚犹如此。其于庶人有何可疑。答申丈(必混)别纸(癸卯)
问小祥后改葬。无变服之节耶。仪节云一如始葬之仪。今亲见尸柩。可无散垂之节耶。
改葬缌举下缅也。礼惟大功以上散垂。故凡改葬必绞其带。然三年之服。练后与大功等。故谓之功衰。大功者则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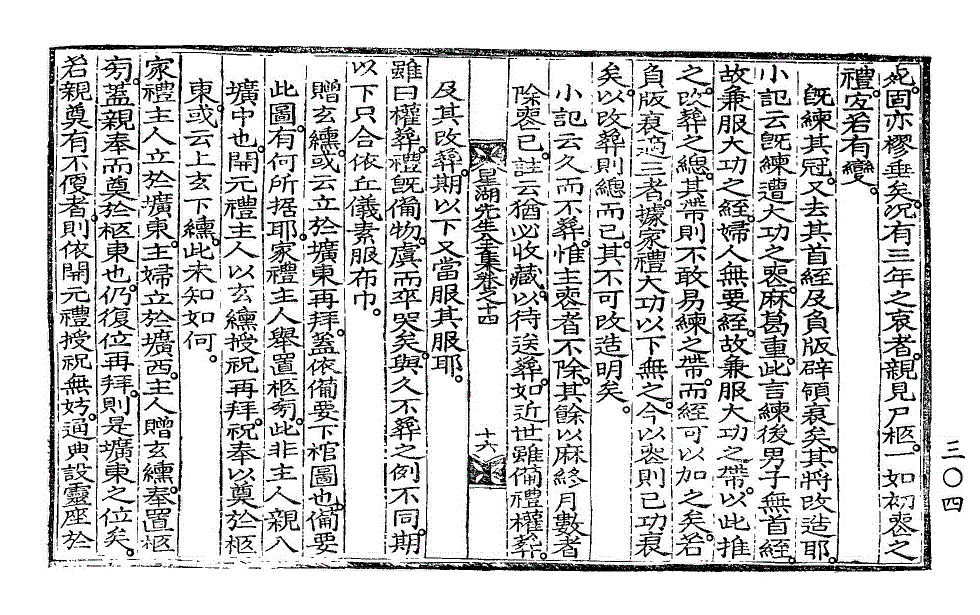 死。固亦樛垂矣。况有三年之哀者。亲见尸柩。一如初丧之礼。宜若有变。
死。固亦樛垂矣。况有三年之哀者。亲见尸柩。一如初丧之礼。宜若有变。既练其冠。又去其首绖及负版辟领衰矣。其将改造耶。
小记云既练遭大功之丧。麻葛重。此言练后男子无首绖。故兼服大功之绖。妇人无要绖。故兼服大功之带。以此推之。改葬之缌。其带则不敢易练之带。而绖可以加之矣。若负版衰适三者。据家礼大功以下无之。今以丧则已功衰矣。以改葬则缌而已。其不可改造明矣。
小记云久而不葬。惟主丧者不除。其馀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已。注云犹必收藏。以待送葬。如近世虽备礼权葬。及其改葬。期以下又当服其服耶。
虽曰权葬。礼既备物。虞而卒哭矣。与久不葬之例不同。期以下只合依丘仪素服布巾。
赠玄纁。或云立于圹东再拜。盖依备要下棺图也。备要此图。有何所据耶。家礼主人举置柩旁。此非主人亲入圹中也。开元礼主人以玄纁授祝再拜。祝奉以奠于柩东。或云上玄下纁。此未知如何。
家礼主人立于圹东。主妇立于圹西。主人赠玄纁。奉置柩旁。盖亲奉而奠于柩东也。仍复位再拜。则是圹东之位矣。若亲奠有不便者。则依开元礼授祝无妨。通典设灵座于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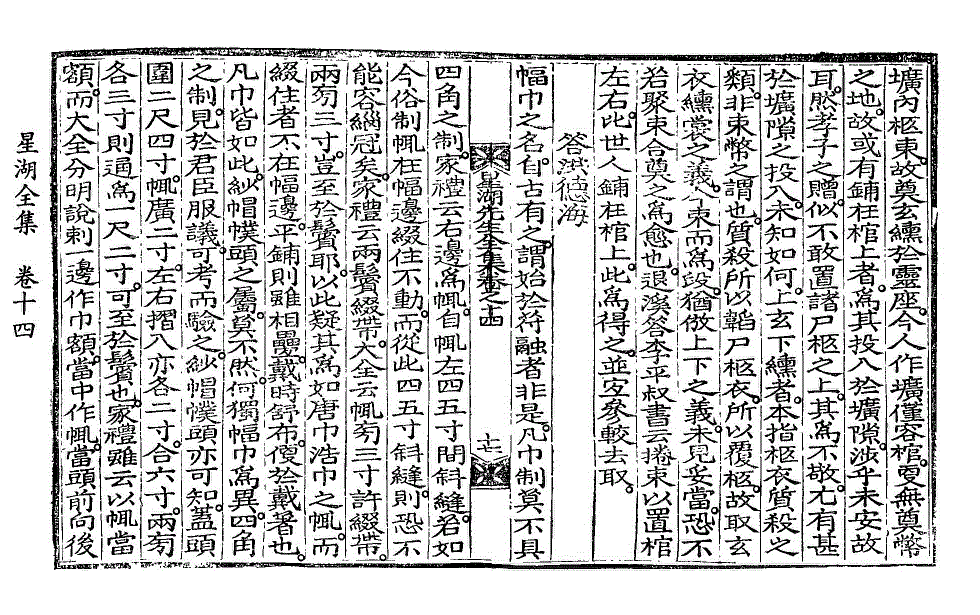 圹内柩东。故奠玄纁于灵座。今人作圹仅容棺。更无奠币之地。故或有铺在棺上者。为其投入于圹隙。涉乎未安故耳。然孝子之赠。似不敢置诸尸柩之上。其为不敬。尤有甚于圹隙之投入。未知如何。上玄下纁者。本指柩衣质杀之类。非束币之谓也。质杀所以韬尸柩衣。所以覆柩。故取玄衣纁裳之义。今束而为段。犹仿上下之义。未见妥当。恐不若聚束合奠之为愈也。退溪答李平叔书云捲束以置棺左右。比世人铺在棺上。此为得之。并宜参较去取。
圹内柩东。故奠玄纁于灵座。今人作圹仅容棺。更无奠币之地。故或有铺在棺上者。为其投入于圹隙。涉乎未安故耳。然孝子之赠。似不敢置诸尸柩之上。其为不敬。尤有甚于圹隙之投入。未知如何。上玄下纁者。本指柩衣质杀之类。非束币之谓也。质杀所以韬尸柩衣。所以覆柩。故取玄衣纁裳之义。今束而为段。犹仿上下之义。未见妥当。恐不若聚束合奠之为愈也。退溪答李平叔书云捲束以置棺左右。比世人铺在棺上。此为得之。并宜参较去取。答洪德海
幅巾之名。自古有之。谓始于苻融者非是。凡巾制莫不具四角之制。家礼云右边为㡇。自㡇左四五寸间斜缝。若如今俗制㡇在幅边缀住不动。而从此四五寸斜缝。则恐不能容缁冠矣。家礼云两鬓缀带。大全云㡇旁三寸许缀带。两旁三寸。岂至于鬓耶。以此疑其为如唐巾浩巾之㡇。而缀住者不在幅边。平铺则虽相叠。戴时舒布。便于戴著也。凡巾皆如此。纱帽幞头之属。莫不然。何独幅巾为异。四角之制。见于君臣服议。可考而验之。纱帽幞头亦可知。盖头围二尺四寸。㡇广二寸。左右摺入亦各二寸。合六寸。两旁各三寸则通为一尺二寸。可至于鬓也。家礼虽云以㡇当额。而大全分明说刺一边作巾额。当中作㡇。当头前向后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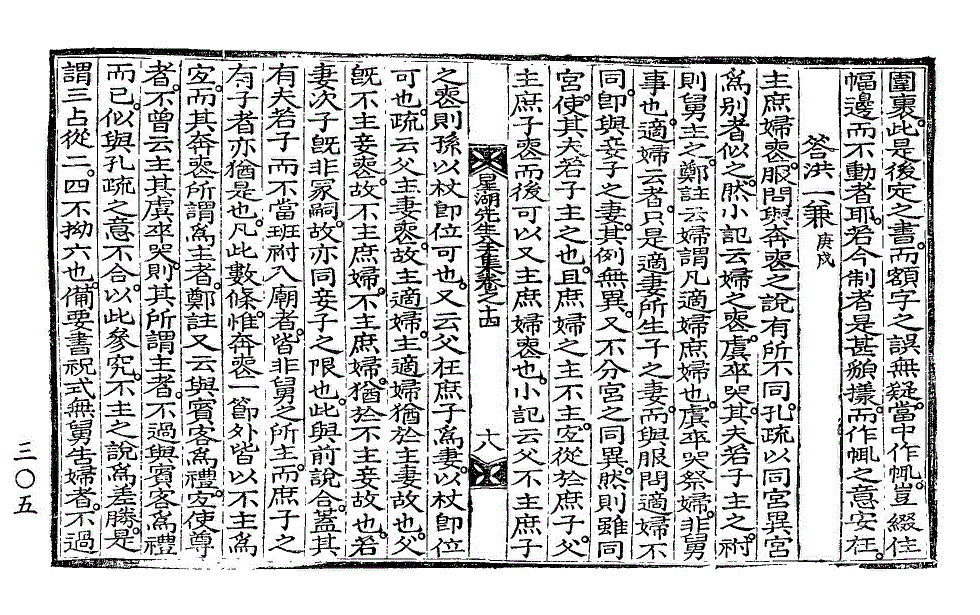 围裹。此是后定之书。而额字之误无疑。当中作㡇。岂缀住幅边而不动者耶。若今制者是甚貌㨾。而作㡇之意安在。
围裹。此是后定之书。而额字之误无疑。当中作㡇。岂缀住幅边而不动者耶。若今制者是甚貌㨾。而作㡇之意安在。答洪一兼(庚戌)
主庶妇丧。服问与奔丧之说有所不同。孔疏以同宫异宫为别者似之。然小记云妇之丧。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则舅主之。郑注云妇谓凡适妇庶妇也。虞卒哭祭妇。非舅事也。适妇云者。只是适妻所生子之妻。而与服问适妇不同。即与妾子之妻。其例无异。又不分宫之同异。然则虽同宫。使其夫若子主之也。且庶妇之主不主。宜从于庶子。父主庶子丧而后可以又主庶妇丧也。小记云父不主庶子之丧则孙以杖即位可也。又云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疏云父主妻丧。故主适妇。主适妇犹于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丧。故不主庶妇。不主庶妇。犹于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既非冢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此与前说合。盖其有夫若子而不当班祔入庙者。皆非舅之所主。而庶子之有子者亦犹是也。凡此数条。惟奔丧一节外皆以不主为宜。而其奔丧所谓为主者。郑注又云与宾客为礼。宜使尊者。不曾云主其虞卒哭。则其所谓主者。不过与宾客为礼而已。似与孔疏之意不合。以此参究。不主之说为差胜。是谓三占从二。四不拗六也。备要书祝式无舅告妇者。不过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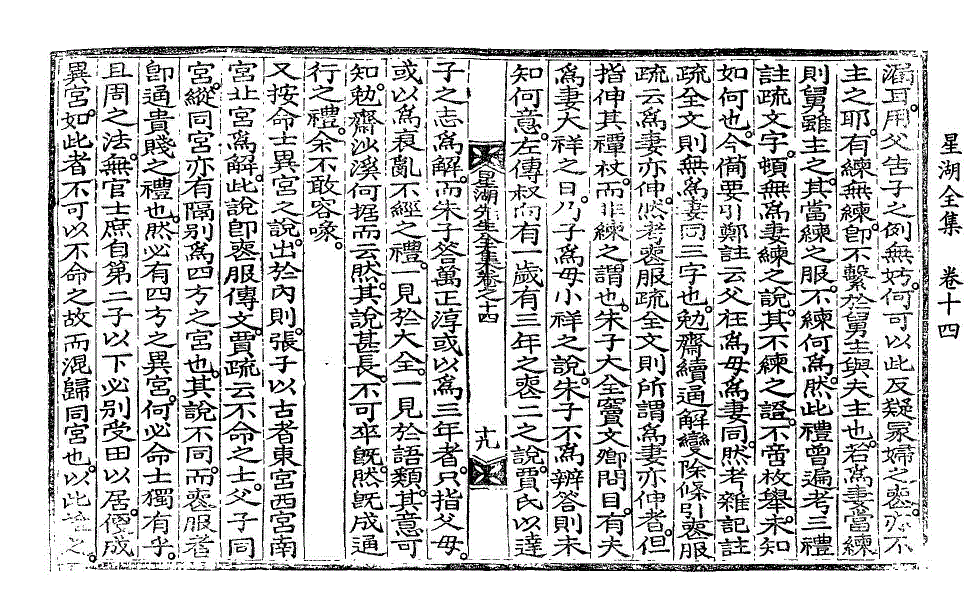 漏耳。用父告子之例无妨。何可以此反疑冢妇之丧。亦不主之耶。有练无练。即不系于舅主与夫主也。若为妻当练则舅虽主之。其当练之服。不练何为。然此礼曾遍考三礼注疏文字。顿无为妻练之说。其不练之證。不啻枚举。未知如何也。今备要引郑注云父在为母为妻同。然考杂记注疏全文则无为妻同三字也。勉斋续通解变除条引丧服疏云为妻亦伸。然考丧服疏全文则所谓为妻亦伸者。但指伸其禫杖。而非练之谓也。朱子大全窦文卿问目。有夫为妻大祥之日。乃子为母小祥之说。朱子不为辨答则未知何意。左传叔向有一岁有三年之丧二之说。贾氏以达子之志为解。而朱子答万正淳或以为三年者。只指父母。或以为衰乱不经之礼。一见于大全。一见于语类。其意可知。勉斋沙溪何据而云然。其说甚长。不可卒既。然既成通行之礼。余不敢容喙。
漏耳。用父告子之例无妨。何可以此反疑冢妇之丧。亦不主之耶。有练无练。即不系于舅主与夫主也。若为妻当练则舅虽主之。其当练之服。不练何为。然此礼曾遍考三礼注疏文字。顿无为妻练之说。其不练之證。不啻枚举。未知如何也。今备要引郑注云父在为母为妻同。然考杂记注疏全文则无为妻同三字也。勉斋续通解变除条引丧服疏云为妻亦伸。然考丧服疏全文则所谓为妻亦伸者。但指伸其禫杖。而非练之谓也。朱子大全窦文卿问目。有夫为妻大祥之日。乃子为母小祥之说。朱子不为辨答则未知何意。左传叔向有一岁有三年之丧二之说。贾氏以达子之志为解。而朱子答万正淳或以为三年者。只指父母。或以为衰乱不经之礼。一见于大全。一见于语类。其意可知。勉斋沙溪何据而云然。其说甚长。不可卒既。然既成通行之礼。余不敢容喙。又按命士异宫之说。出于内则。张子以古者东宫西宫南宫北宫为解。此说即丧服传文。贾疏云不命之士。父子同宫。纵同宫亦有隔别为四方之宫也。其说不同。而丧服者即通贵贱之礼也。然必有四方之异宫。何必命士独有乎。且周之法。无官士庶自第二子以下必别受田以居。便成异宫。如此者不可以不命之故而混归同宫也。以此推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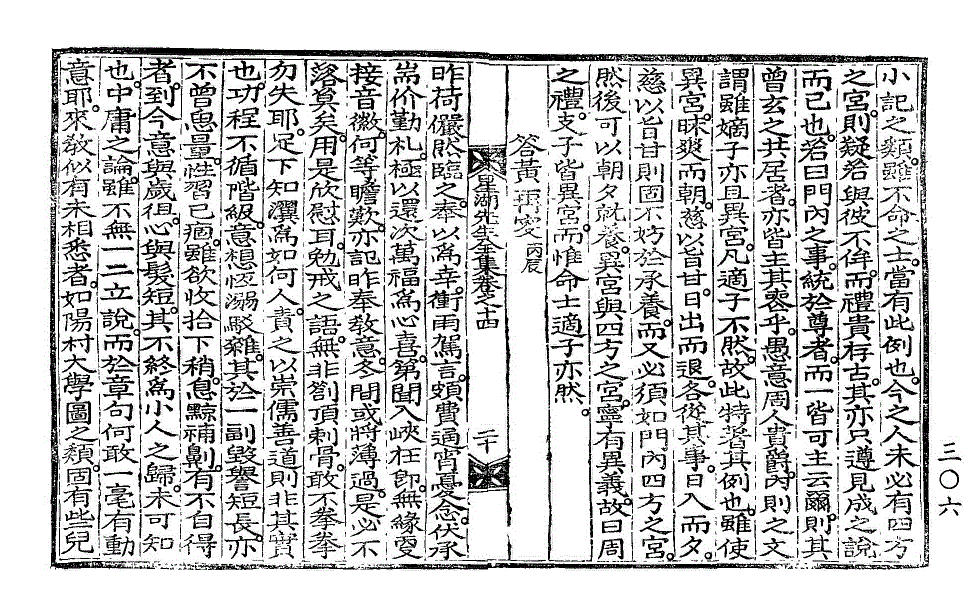 小记之类。虽不命之士。当有此例也。今之人未必有四方之宫。则疑若与彼不侔。而礼贵存古。其亦只遵见成之说而已也。若曰门内之事。统于尊者。而一皆可主云尔。则其曾玄之共居者。亦皆主其丧乎。愚意周人贵爵。内则之文谓虽嫡子亦且异宫。凡适子不然。故此特著其例也。虽使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从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则固不妨于承养。而又必须如门内四方之宫。然后可以朝夕就养。异宫与四方之宫。宁有异义。故曰周之礼。支子皆异宫。而惟命士适子亦然。
小记之类。虽不命之士。当有此例也。今之人未必有四方之宫。则疑若与彼不侔。而礼贵存古。其亦只遵见成之说而已也。若曰门内之事。统于尊者。而一皆可主云尔。则其曾玄之共居者。亦皆主其丧乎。愚意周人贵爵。内则之文谓虽嫡子亦且异宫。凡适子不然。故此特著其例也。虽使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从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则固不妨于承养。而又必须如门内四方之宫。然后可以朝夕就养。异宫与四方之宫。宁有异义。故曰周之礼。支子皆异宫。而惟命士适子亦然。答黄再叟(丙辰)
昨荷俨然临之。奉以为幸。冲雨驾言。颇费通宵忧念。伏承耑价勤札。极以还次万福为心喜。第闻入峡在即。无缘更接音徽。何等瞻叹。亦记昨奉教意。冬间或将薄过。是必不落莫矣。用是欣慰耳。勉戒之语。无非劄顶刺骨。敢不拳拳勿失耶。足下知瀷为如何人。责之以崇儒善道则非其实也。功程不循阶级。意想恒溺驳杂。其于一副毁誉短长。亦不曾思量。性习已痼。虽欲收拾下稍。息黥补劓。有不自得者。到今意与岁徂。心与发短。其不终为小人之归。未可知也。中庸之论。虽不无一二立说。而于章句何敢一毫有动意耶。来教似有未相悉者。如阳村大学图之类。固有些儿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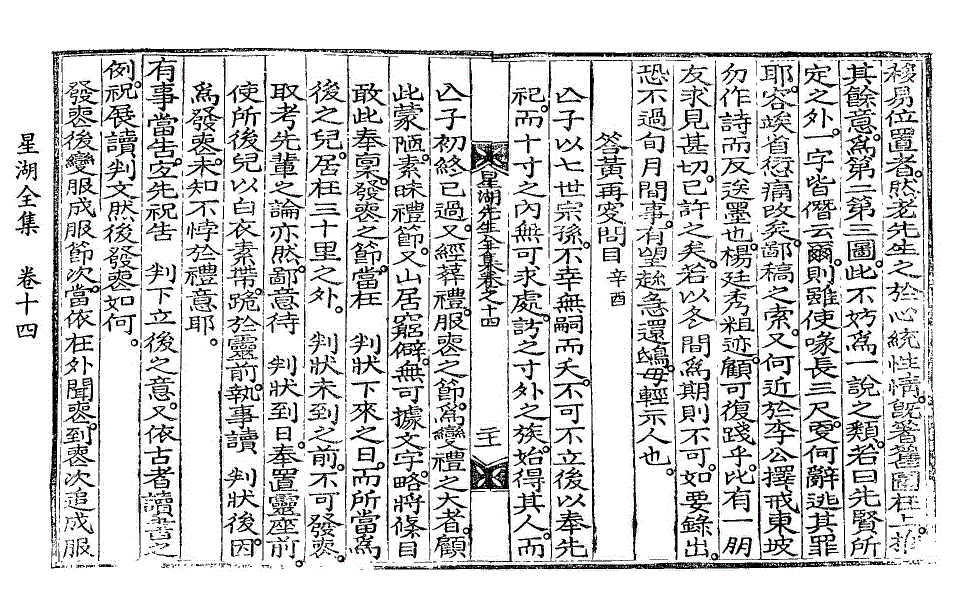 移易位置者。然老先生之于心统性情。既著旧图在上。推其馀意。为第二第三图。此不妨为一说之类。若曰先贤所定之外。一字皆僭云尔。则虽使喙长三尺。更何辞逃其罪耶。容俟省愆痛改矣。鄙稿之索。又何近于李公择戒东坡勿作诗而反送墨也。杨廷秀粗迹。顾可复践乎。比有一朋友求见甚切。已许之矣。若以冬间为期则不可。如要录出。恐不过旬月间事。有望趁急还鸱。毋轻示人也。
移易位置者。然老先生之于心统性情。既著旧图在上。推其馀意。为第二第三图。此不妨为一说之类。若曰先贤所定之外。一字皆僭云尔。则虽使喙长三尺。更何辞逃其罪耶。容俟省愆痛改矣。鄙稿之索。又何近于李公择戒东坡勿作诗而反送墨也。杨廷秀粗迹。顾可复践乎。比有一朋友求见甚切。已许之矣。若以冬间为期则不可。如要录出。恐不过旬月间事。有望趁急还鸱。毋轻示人也。答黄再叟问目(辛酉)
亡子以七世宗孙。不幸无嗣而夭。不可不立后以奉先祀。而十寸之内无可求处。访之寸外之族。始得其人。而亡子初终已过。又经葬礼。服丧之节。为变礼之大者。顾此蒙陋。素昧礼节。又山居穷僻。无可据文字。略将条目敢此奉禀。发丧之节。当在 判状下来之日。而所当为后之儿。居在三十里之外。 判状未到之前。不可发丧。取考先辈之论亦然。鄙意待 判状到日。奉置灵座前。使所后儿以白衣素带。跪于灵前。执事读 判状后。因为发丧。未知不悖于礼意耶。
有事当告。宜先祝告 判下立后之意。又依古者读书之例。祝展读判文然后发丧如何。
发丧后变服成服节次。当依在外闻丧。到丧次追成服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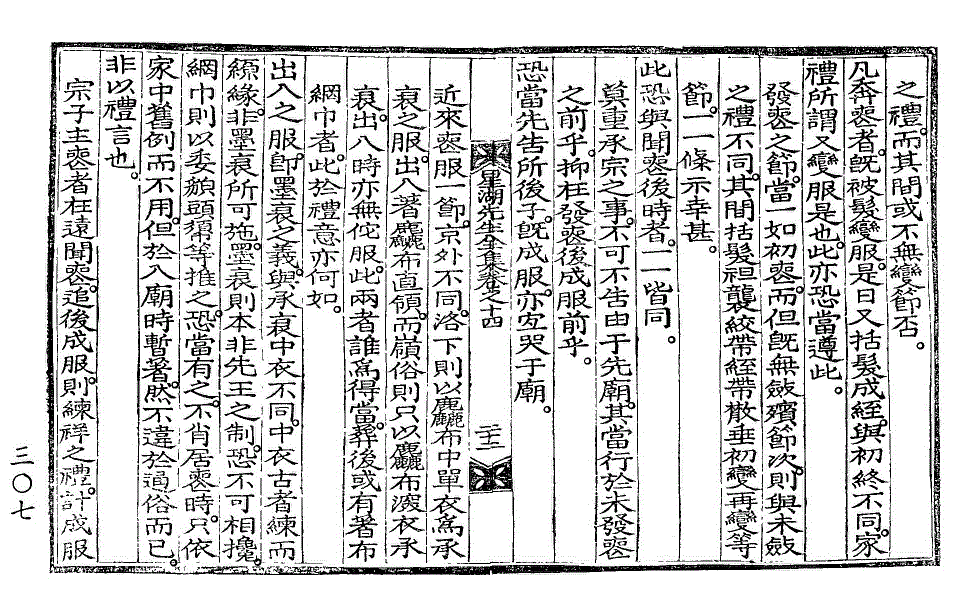 之礼。而其间或不无变节否。
之礼。而其间或不无变节否。凡奔丧者。既被发变服。是日又括发成绖。与初终不同。家礼所谓又变服是也。此亦恐当遵此。
发丧之节。当一如初丧。而但既无敛殡节次。则与未敛之礼不同。其间括发袒袭绞带绖带散垂初变再变等节。一一条示幸甚。
此恐与闻丧后时者。一一皆同。
莫重承宗之事。不可不告由于先庙。其当行于未发丧之前乎。抑在发丧后成服前乎。
恐当先告所后子。既成服。亦宜哭于庙。
近来丧服一节。京外不同。洛下则以粗布中单衣为承衰之服。出入著粗布直领。而岭俗则只以粗布深衣承衰。出入时亦无佗服。此两者谁为得当。葬后或有著布网巾者。此于礼意亦何如。
出入之服。即墨衰之义。与承衰中衣不同。中衣古者练而縓缘。非墨衰所可施。墨衰则本非先王之制。恐不可相搀。网巾则以委貌头𢄼等推之。恐当有之。不肖居丧时。只依家中旧例而不用。但于入庙时暂著。然不违于通俗而已。非以礼言也。
宗子主丧者在远闻丧。追后成服。则练祥之礼。计成服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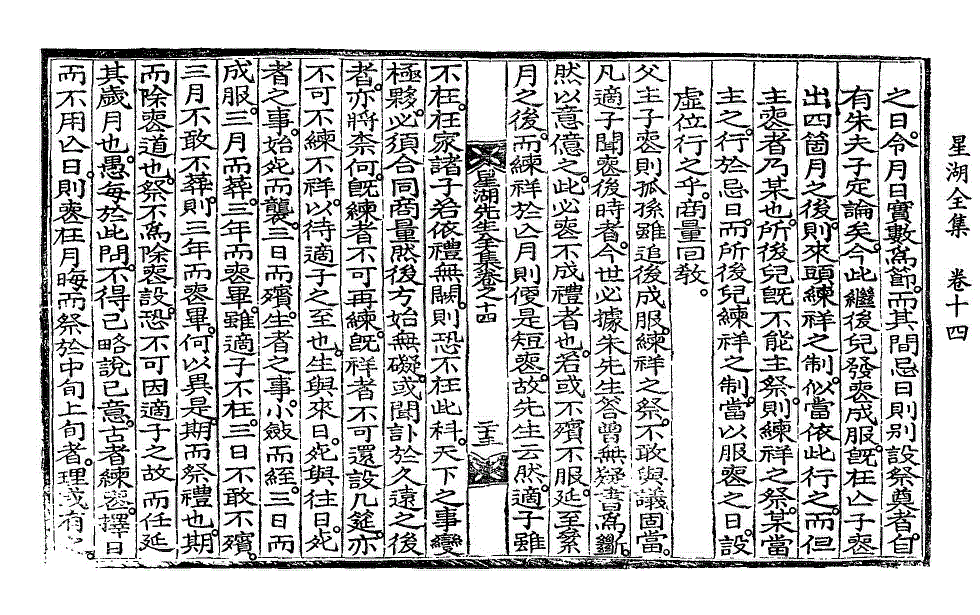 之日。令月日实数为节。而其间忌日则别设祭奠者。自有朱夫子定论矣。今此继后儿发丧成服。既在亡子丧出四个月之后。则来头练祥之制。似当依此行之。而但主丧者乃某也。所后儿既不能主祭。则练祥之祭。某当主之。行于忌日。而所后儿练祥之制。当以服丧之日。设虚位行之乎。商量回教。
之日。令月日实数为节。而其间忌日则别设祭奠者。自有朱夫子定论矣。今此继后儿发丧成服。既在亡子丧出四个月之后。则来头练祥之制。似当依此行之。而但主丧者乃某也。所后儿既不能主祭。则练祥之祭。某当主之。行于忌日。而所后儿练祥之制。当以服丧之日。设虚位行之乎。商量回教。父主子丧则孤孙虽追后成服。练祥之祭。不敢与议固当。凡适子闻丧后时者。今世必据朱先生答曾无疑书为断。然以意亿之。此必丧不成礼者也。若或不殡不服。延至累月之后。而练祥于亡月则便是短丧。故先生云然。适子虽不在。在家诸子若依礼无阙。则恐不在此科。天下之事变极夥。必须合同商量然后方始无碍。或闻讣于久远之后者。亦将柰何。既练者不可再练。既祥者不可还设几筵。亦不可不练不祥。以待适子之至也。生与来日。死与往日。死者之事。始死而袭。三日而殡。生者之事。小敛而绖。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三年而丧毕。虽适子不在。三日不敢不殡。三月不敢不葬。则三年而丧毕。何以异是。期而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祭不为除丧设。恐不可因适子之故而任延其岁月也。愚每于此问。不得已略说己意。古者练丧。择日而不用亡日。则丧在月晦而祭于中旬上旬者。理或有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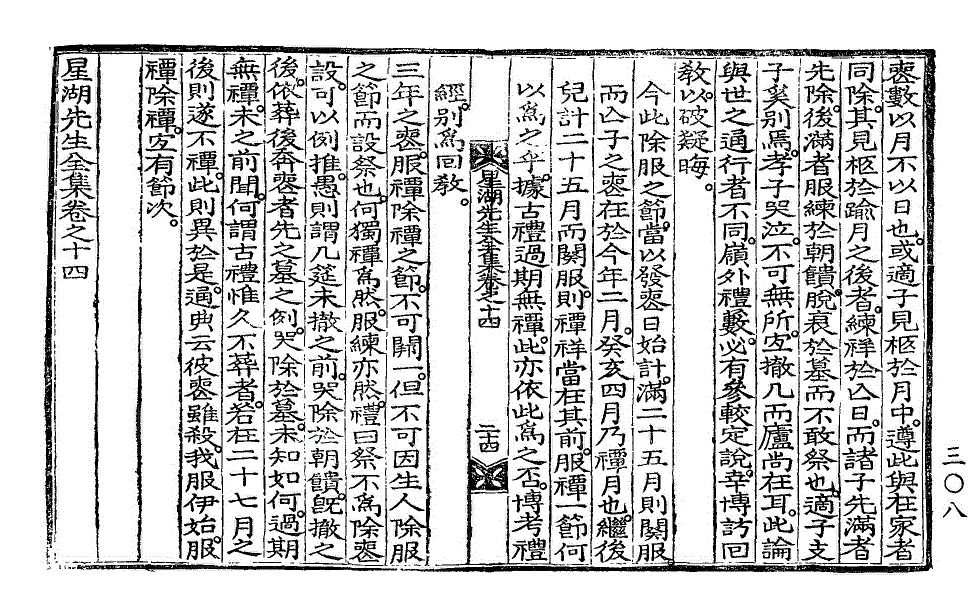 丧数以月不以日也。或适子见柩于月中。遵此与在家者同除。其见柩于踰月之后者。练祥于亡日。而诸子先满者先除。后满者服练于朝馈。脱衰于墓而不敢祭也。适子支子奚别焉。孝子哭泣。不可无所。宜撤几而庐尚在耳。此论与世之通行者不同。岭外礼薮。必有参较定说。幸博访回教。以破疑晦。
丧数以月不以日也。或适子见柩于月中。遵此与在家者同除。其见柩于踰月之后者。练祥于亡日。而诸子先满者先除。后满者服练于朝馈。脱衰于墓而不敢祭也。适子支子奚别焉。孝子哭泣。不可无所。宜撤几而庐尚在耳。此论与世之通行者不同。岭外礼薮。必有参较定说。幸博访回教。以破疑晦。今此除服之节。当以发丧日始计。满二十五月则阕服。而亡子之丧在于今年二月。癸亥四月乃禫月也。继后儿计二十五月而阕服。则禫祥当在其前。服禫一节何以为之乎。据古礼过期无禫。此亦依此为之否。博考礼经。别为回教。
三年之丧。服禫除禫之节。不可阙一。但不可因生人除服之节而设祭也。何独禫为然。服练亦然。礼曰祭不为除丧设。可以例推。愚则谓几筵未撤之前。哭除于朝馈。既撤之后。依葬后奔丧者先之墓之例。哭除于墓。未知如何。过期无禫。未之前闻。何谓古礼惟久不葬者。若在二十七月之后则遂不禫。此则异于是。通典云彼丧虽杀。我服伊始。服禫除禫。宜有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