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x 页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书
书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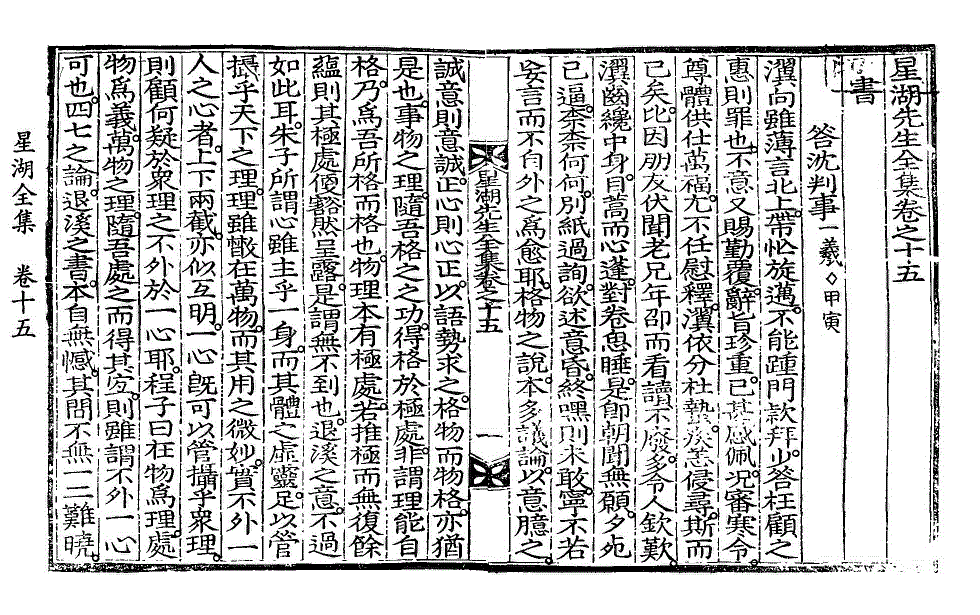 答沈判事(一羲○甲寅)
答沈判事(一羲○甲寅)瀷向虽薄言北上。带忙旋迈。不能踵门款拜。少答枉顾之惠则罪也。不意又赐勤覆。辞旨珍重。已甚感佩。况审寒令。尊体供仕万福。尤不任慰释。瀷依分杜蛰。疾恙侵寻。斯而已矣。比因朋友伏闻老兄年卲而看读不废。多令人钦叹。瀷齿才中身。目蒿而心蓬。对卷思睡。是即朝闻无愿。夕死已逼。柰柰何何。别纸过询。欲述意昏。终嘿则未敢。宁不若妄言而不自外之为愈耶。格物之说。本多议论。以意臆之。诚意则意诚。正心则心正。以语势求之。格物而物格。亦犹是也。事物之理。随吾格之之功。得格于极处。非谓理能自格。乃为吾所格而格也。物理本有极处。若推极而无复馀蕴则其极处便豁然呈露。是谓无不到也。退溪之意。不过如此耳。朱子所谓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摄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一人之心者。上下两截。亦似互明。一心既可以管摄乎众理。则顾何疑于众理之不外于一心耶。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万物之理。随吾处之而得其宜。则虽谓不外一心可也。四七之论。退溪之书。本自无憾。其间不无一二难晓。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09L 页
 如欲一一勘合无痕则终不可归一。其答高峰以本然及气质之性。比同于四与七而为分属理气之證则有不然者。本然气质。非有二性。即就气质性中指出纯善者曰本然之性。若然以四为七中善一边者。其意何别。至于高峰后说。退溪有烂漫同归之叹。而乃以舜之怒孟子之喜之类为理发。而与四端无异。是依旧前说之不变。若果圣贤之七情宜属之理发。则七者终非气发一边事。近世儒者虽主善一边之说。而却又引朱子四端亦有恶之训。合成完论。亦可笑。若四者亦有恶则所谓善一边者。不辨而破矣。高峰之以七属气。而却以纯善者属理。亦犹夫近世之以四为善一边。而却谓四亦有恶。抑退溪所谓独得昭旷之源而一出于正者何居乎。朱子谓理动故气动。理与气固无先后之可言。但其推去时。却似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岂有气先发之道也。四七之分属理气。实与人心道心之或生或原不异。四是从理直遂故曰理发。七是因吾形气而发故曰气发。非谓气先发而理方去乘之也。形气者即吾之私有。贴在人心之人字。饥饱寒燠是人心。而因形气有者也。顺之则喜逆之则怒之类。即七情是谓气发也。至若舜之怒孟子之喜。虽若不涉于形气之私。别是一义。七情之说。本出礼运。其言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
如欲一一勘合无痕则终不可归一。其答高峰以本然及气质之性。比同于四与七而为分属理气之證则有不然者。本然气质。非有二性。即就气质性中指出纯善者曰本然之性。若然以四为七中善一边者。其意何别。至于高峰后说。退溪有烂漫同归之叹。而乃以舜之怒孟子之喜之类为理发。而与四端无异。是依旧前说之不变。若果圣贤之七情宜属之理发。则七者终非气发一边事。近世儒者虽主善一边之说。而却又引朱子四端亦有恶之训。合成完论。亦可笑。若四者亦有恶则所谓善一边者。不辨而破矣。高峰之以七属气。而却以纯善者属理。亦犹夫近世之以四为善一边。而却谓四亦有恶。抑退溪所谓独得昭旷之源而一出于正者何居乎。朱子谓理动故气动。理与气固无先后之可言。但其推去时。却似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岂有气先发之道也。四七之分属理气。实与人心道心之或生或原不异。四是从理直遂故曰理发。七是因吾形气而发故曰气发。非谓气先发而理方去乘之也。形气者即吾之私有。贴在人心之人字。饥饱寒燠是人心。而因形气有者也。顺之则喜逆之则怒之类。即七情是谓气发也。至若舜之怒孟子之喜。虽若不涉于形气之私。别是一义。七情之说。本出礼运。其言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0H 页
 一身。非意之也。明于其利。达于其患。故众人之形气。视同己私。患利之感。如劄厥身。而人之喜怒。即己之喜怒也。迹若差别。苗脉则同。岂可以此遂归之理发乎。此其槩也。所谓性发心发云者。心统性情。故未发统性。既发统情。意者即统情之名也。合而言则意亦心也。故曰统性情。分而言则指其发处曰意也。心气而性理也。理与气相离不得。理发为情。气必同发。故以寂感分属之。在理则性为寂发而为情者。是感通也。在气则心之未发为寂发而为意。是感通也。二者寂则同寂。感则同感。非以心为性。即心寂而包性在中也。若以形而上下言之。形而上曰道。道属理。形而下曰器。器属气。心是该性则器之载道也。来说似然。然神明之心。不可以形为谕。故朱子云尔。若以心之虚灵。归之于天之所为。此虽宜然。夫天之化生万物。理气而已。如又曰天之所为如何而如此云尔。则其可舍理气而说得破耶。心是活物。故自有此虚灵。如禽兽之心。其有私无公。虽与人之道心者不同。既有知觉。不可谓全无虚灵也。其见利而趋。知祸而避。非虚灵而何。虚灵者知觉之体也。若全无虚灵。又安从而有知觉之用耶。但禀气之偏。不离于形气之私。故虚具灵应之妙。不能如人之为耳。张子性心之论。只是言其名目。非有先后之别也。不然则不但性先心
一身。非意之也。明于其利。达于其患。故众人之形气。视同己私。患利之感。如劄厥身。而人之喜怒。即己之喜怒也。迹若差别。苗脉则同。岂可以此遂归之理发乎。此其槩也。所谓性发心发云者。心统性情。故未发统性。既发统情。意者即统情之名也。合而言则意亦心也。故曰统性情。分而言则指其发处曰意也。心气而性理也。理与气相离不得。理发为情。气必同发。故以寂感分属之。在理则性为寂发而为情者。是感通也。在气则心之未发为寂发而为意。是感通也。二者寂则同寂。感则同感。非以心为性。即心寂而包性在中也。若以形而上下言之。形而上曰道。道属理。形而下曰器。器属气。心是该性则器之载道也。来说似然。然神明之心。不可以形为谕。故朱子云尔。若以心之虚灵。归之于天之所为。此虽宜然。夫天之化生万物。理气而已。如又曰天之所为如何而如此云尔。则其可舍理气而说得破耶。心是活物。故自有此虚灵。如禽兽之心。其有私无公。虽与人之道心者不同。既有知觉。不可谓全无虚灵也。其见利而趋。知祸而避。非虚灵而何。虚灵者知觉之体也。若全无虚灵。又安从而有知觉之用耶。但禀气之偏。不离于形气之私。故虚具灵应之妙。不能如人之为耳。张子性心之论。只是言其名目。非有先后之别也。不然则不但性先心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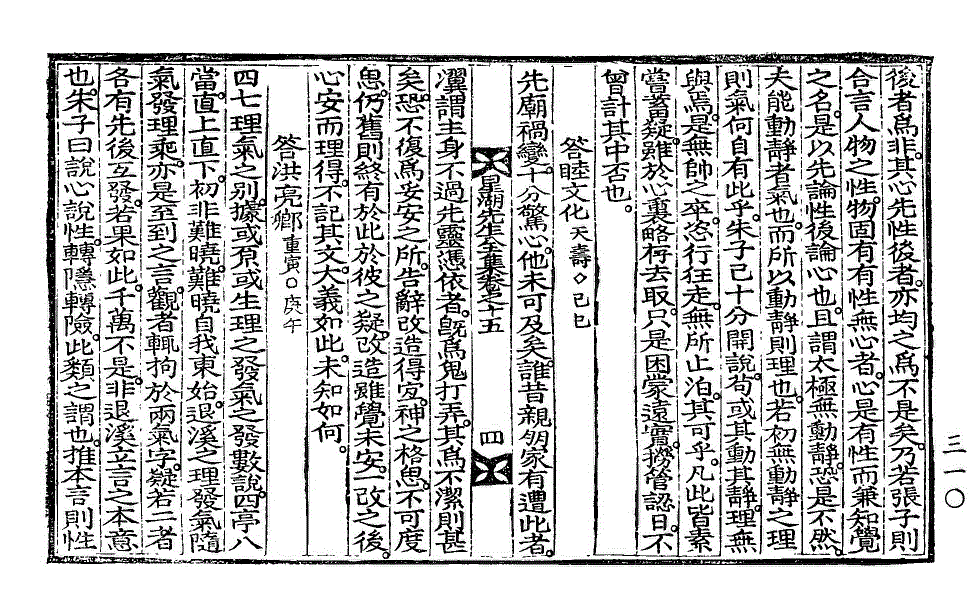 后者为非。其心先性后者。亦均之为不是矣。乃若张子则合言人物之性。物固有有性无心者。心是有性而兼知觉之名。是以先论性后论心也。且谓太极无动静。恐是不然。夫能动静者气也。而所以动静则理也。若初无动静之理则气何自有此乎。朱子已十分开说。苟或其动其静。理无与焉。是无帅之卒。恣行狂走。无所止泊。其可乎。凡此皆素尝蓄疑。虽于心里略存去取。只是困蒙远实。捞管认日。不曾计其中否也。
后者为非。其心先性后者。亦均之为不是矣。乃若张子则合言人物之性。物固有有性无心者。心是有性而兼知觉之名。是以先论性后论心也。且谓太极无动静。恐是不然。夫能动静者气也。而所以动静则理也。若初无动静之理则气何自有此乎。朱子已十分开说。苟或其动其静。理无与焉。是无帅之卒。恣行狂走。无所止泊。其可乎。凡此皆素尝蓄疑。虽于心里略存去取。只是困蒙远实。捞管认日。不曾计其中否也。答睦文化(天寿○己巳)
先庙祸变。十分惊心。他未可及矣。谁昔亲朋家有遭此者。瀷谓主身不过先灵凭依者。既为鬼打弄。其为不洁则甚矣。恐不复为妥安之所。告辞改造得宜。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仍旧则终有于此于彼之疑。改造虽觉未安。一改之后。心安而理得。不记其文。大义如此。未知如何。
答洪亮卿(重寅○庚午)
四七理气之别。据或原或生理之发气之发数说。四亭八当。直上直下。初非难晓。难晓自我东始。退溪之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亦是至到之言。观者辄拘于两气字。疑若二者各有先后互发。若果如此。千万不是。非退溪立言之本意也。朱子曰说心说性。转隐转险。此类之谓也。推本言则性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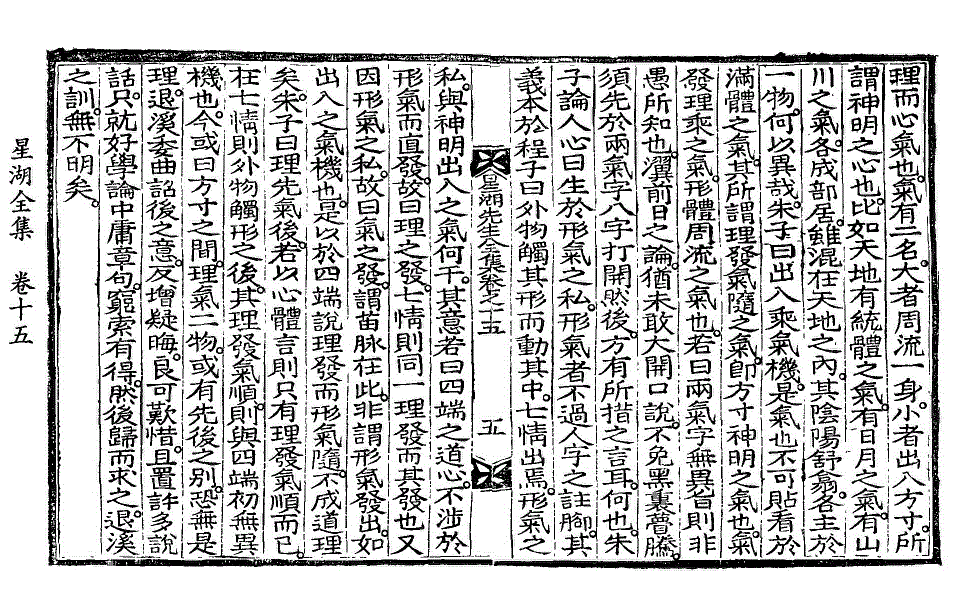 理而心气也。气有二名。大者周流一身。小者出入方寸。所谓神明之心也。比如天地有统体之气。有日月之气。有山川之气。各成部居。虽混在天地之内。其阴阳舒翕。各主于一物。何以异哉。朱子曰出入乘气机。是气也不可贴看于满体之气。其所谓理发气随之气。即方寸神明之气也。气发理乘之气。形体周流之气也。若曰两气字无异旨则非愚所知也。瀷前日之论。犹未敢大开口说。不免黑里瞢腾。须先于两气字八字打开然后。方有所措之言耳。何也。朱子论人心曰生于形气之私。形气者不过人字之注脚。其义本于程子曰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七情出焉。形气之私。与神明出入之气何干。其意若曰四端之道心。不涉于形气而直发。故曰理之发。七情则同一理发而其发也又因形气之私。故曰气之发。谓苗脉在此。非谓形气发出。如出入之气机也。是以于四端说理发而形气随。不成道理矣。朱子曰理先气后。若以心体言则只有理发气顺而已。在七情则外物触形之后。其理发气顺。则与四端初无异机也。今或曰方寸之间。理气二物。或有先后之别。恐无是理。退溪委曲诏后之意。反增疑晦。良可叹惜。且置许多说话。只就好学论中庸章句。穷索有得。然后归而求之。退溪之训。无不明矣。
理而心气也。气有二名。大者周流一身。小者出入方寸。所谓神明之心也。比如天地有统体之气。有日月之气。有山川之气。各成部居。虽混在天地之内。其阴阳舒翕。各主于一物。何以异哉。朱子曰出入乘气机。是气也不可贴看于满体之气。其所谓理发气随之气。即方寸神明之气也。气发理乘之气。形体周流之气也。若曰两气字无异旨则非愚所知也。瀷前日之论。犹未敢大开口说。不免黑里瞢腾。须先于两气字八字打开然后。方有所措之言耳。何也。朱子论人心曰生于形气之私。形气者不过人字之注脚。其义本于程子曰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七情出焉。形气之私。与神明出入之气何干。其意若曰四端之道心。不涉于形气而直发。故曰理之发。七情则同一理发而其发也又因形气之私。故曰气之发。谓苗脉在此。非谓形气发出。如出入之气机也。是以于四端说理发而形气随。不成道理矣。朱子曰理先气后。若以心体言则只有理发气顺而已。在七情则外物触形之后。其理发气顺。则与四端初无异机也。今或曰方寸之间。理气二物。或有先后之别。恐无是理。退溪委曲诏后之意。反增疑晦。良可叹惜。且置许多说话。只就好学论中庸章句。穷索有得。然后归而求之。退溪之训。无不明矣。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1L 页
 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此朱子说也。从理在物上说则只须言气质之性。理自有为而质各不同。故在水为水之性。在火为火之性。牛为牛性。马为马性。比如水一也。和丹则渥然。和墨则黟然。此理无不通。而为气所局。以此看其说亦有理。
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此朱子说也。从理在物上说则只须言气质之性。理自有为而质各不同。故在水为水之性。在火为火之性。牛为牛性。马为马性。比如水一也。和丹则渥然。和墨则黟然。此理无不通。而为气所局。以此看其说亦有理。活看之诲。谨当遵矣。然彼方谓四乃七中善一边。以此下言。无乃助扬其波澜耶。其他又不无可疑处。答李平叔一书。却似混其分界。一种人据为后定之论。须该考近世儒术。乃曰善一边固至矣。朱子有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之说。补此方为完备。若然何谓善一边。其迷惑如此。
外感内应。四七同然。故赤子入井则恻隐之心生。外物触形气则七情出也。以内应言则理动而气顺。亦四七同然。故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但七情添形气一节。于此下一私字则理发之不与于形气可知。形气者私也。私不待教。故不但贤愚同有。虽禽兽虫鱼亦同有。但闻四端灭息。不闻七情全塞也。饱煖则喜。饥寒则哀。岂学而能者耶。恻隐羞恶之类。其端虽见。不克充扩。微者愈微矣。惟贤圣之七情。或有不涉于形气之私者。此则新编中备论之。此圣贤推广之极功。至于万物一体。气与相贯。别是一般议论。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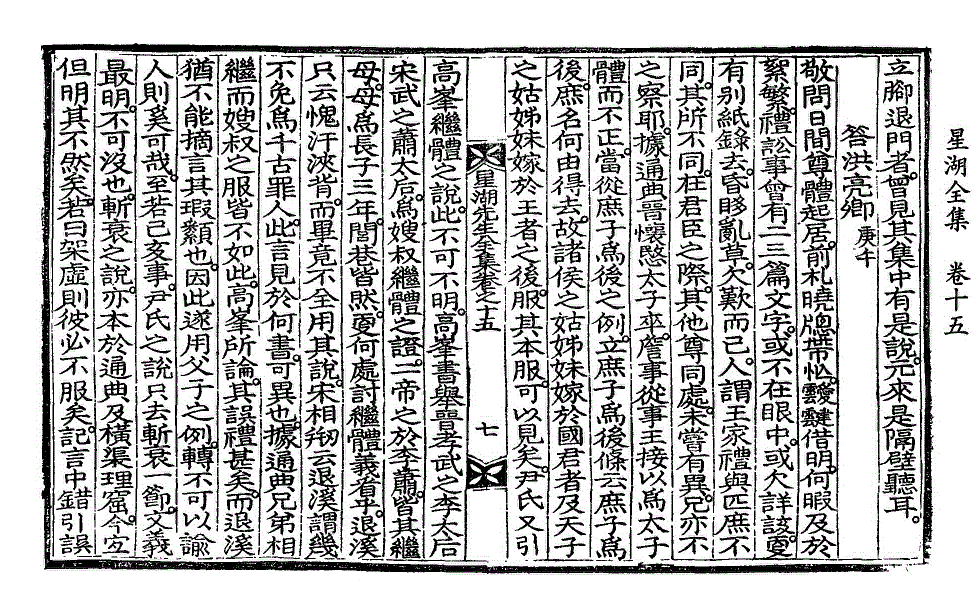 立脚退门者。曾见其集中有是说。元来是隔壁听耳。
立脚退门者。曾见其集中有是说。元来是隔壁听耳。答洪亮卿(庚午)
敬问日间尊体起居。前札晓窗带忙。叆叇借明。何暇及于絮繁。礼讼事曾有二三篇文字。或不在眼中。或欠详该。更有别纸录去。昏眵乱草。欠叹而已。人谓王家礼与匹庶不同。其所不同。在君臣之际。其他尊同处。未尝有异。兄亦不之察耶。据通典晋怀悯太子卒。詹事从事王接以为太子体而不正。当从庶子为后之例。立庶子为后条云庶子为后。庶名何由得去。故诸侯之姑姊妹嫁于国君者及天子之姑姊妹嫁于王者之后。服其本服。可以见矣。尹氏又引高峰继体之说。此不可不明。高峰书举晋孝武之李太后宋武之萧太后。为嫂叔继体之證。二帝之于李,萧。皆其继母。母为长子三年。闾巷皆然。更何处讨继体义看乎。退溪只云愧汗浃背。而毕竟不全用其说。宋相刱云退溪谓几不免为千古罪人。此言见于何书。可异也。据通典兄弟相继而嫂叔之服皆不如此。高峰所论。其误礼甚矣。而退溪犹不能摘言其瑕颣也。因此遂用父子之例。转不可以谕人则奚可哉。至若己亥事。尹氏之说只去斩衰一节。文义最明。不可没也。斩衰之说。亦本于通典及横渠理窟。今宜但明其不然矣。若曰架虚则彼必不服矣。记言中错引误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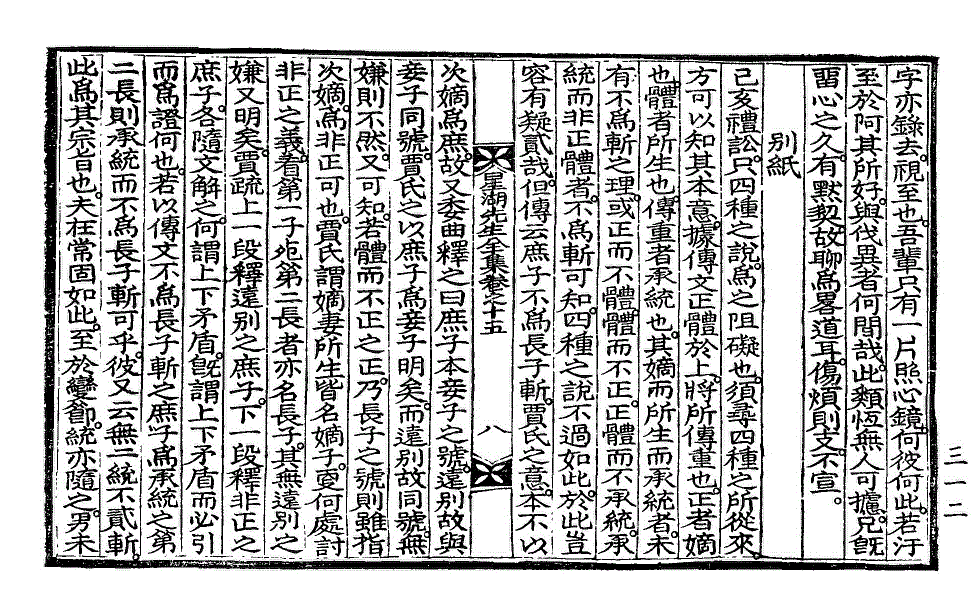 字亦录去。视至也。吾辈只有一片照心镜。何彼何此。若污至于阿其所好。与伐异者何间哉。此类恒无人可摅。兄既留心之久。有默契。故聊为略道耳。伤烦则支。不宣。
字亦录去。视至也。吾辈只有一片照心镜。何彼何此。若污至于阿其所好。与伐异者何间哉。此类恒无人可摅。兄既留心之久。有默契。故聊为略道耳。伤烦则支。不宣。别纸
己亥礼讼。只四种之说。为之阻碍也。须寻四种之所从来。方可以知其本意。据传文正体于上。将所传重也。正者嫡也。体者所生也。传重者承统也。其嫡而所生而承统者。未有不为斩之理。或正而不体。体而不正。正体而不承统。承统而非正体者。不为斩可知。四种之说不过如此。于此岂容有疑贰哉。但传云庶子不为长子斩。贾氏之意。本不以次嫡为庶。故又委曲释之曰庶子本妾子之号。远别故与妾子同号。贾氏之以庶子为妾子明矣。而远别故同号。无嫌则不然。又可知。若体而不正之正。乃长子之号则虽指次嫡。为非正可也。贾氏谓嫡妻所生皆名嫡子。更何处讨非正之义。看第一子死第二长者亦名长子。其无远别之嫌又明矣。贾疏上一段释远别之庶子。下一段释非正之庶子。各随文解之。何谓上下矛盾。既谓上下矛盾而必引而为證何也。若以传文不为长子斩之庶子为承统之第二长则承统而不为长子斩可乎。彼又云无二统不贰斩。此为其宗旨也。夫在常固如此。至于变节。统亦随之。男未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3H 页
 出继女在室。已统于父而服斩矣。后至出继则又统于所后而斩。适人则又统于夫而斩。亦可谓二统而贰斩乎。若宗统如此。嫡统在彼。独不为二统之归乎。彼又为八大君二十四年之说。人谓必无之理者亦误。设令继母相继而亡至七至八则其可以年数之多而不服乎。又或父先亡而后祖亡而后曾祖亡而后高祖亡。又或君亡而后嗣君亡则虽至八世之远。恐不可不服斩。此何以异例。彼又曰必得次长不为庶子之證然后可从。据三礼正文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者凡三见。此及礼记两条是也。远别故称庶。其他无嫌者。嫡庶之别甚明。姑举一二。丧服不杖章大夫之庶子为嫡昆弟。疏云妾子故言庶。若嫡妻所生第二以下。当直云昆弟。不言庶也。内则云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嫡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小记云妇之丧虞卒哭。夫若子主之。祔则舅主之。郑注云凡妇谓嫡妇庶妇。若是冢妇则舅当主之。其夫若子安得为主。如是而犹谓不可从乎。彼又曰第一子殇不为斩。故为第二长者斩。若然此当为第一义。古人反覆详释。而独不及此何也。传不言注不言疏不言。而必穷寻意虑之外。为不斩之證。亦辛苦矣。凡八岁以上皆为殇。既在童幼而死。恐不可以当第一之目。况殇服条公及大夫为嫡子之长殇大功。凡服降
出继女在室。已统于父而服斩矣。后至出继则又统于所后而斩。适人则又统于夫而斩。亦可谓二统而贰斩乎。若宗统如此。嫡统在彼。独不为二统之归乎。彼又为八大君二十四年之说。人谓必无之理者亦误。设令继母相继而亡至七至八则其可以年数之多而不服乎。又或父先亡而后祖亡而后曾祖亡而后高祖亡。又或君亡而后嗣君亡则虽至八世之远。恐不可不服斩。此何以异例。彼又曰必得次长不为庶子之證然后可从。据三礼正文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者凡三见。此及礼记两条是也。远别故称庶。其他无嫌者。嫡庶之别甚明。姑举一二。丧服不杖章大夫之庶子为嫡昆弟。疏云妾子故言庶。若嫡妻所生第二以下。当直云昆弟。不言庶也。内则云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嫡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小记云妇之丧虞卒哭。夫若子主之。祔则舅主之。郑注云凡妇谓嫡妇庶妇。若是冢妇则舅当主之。其夫若子安得为主。如是而犹谓不可从乎。彼又曰第一子殇不为斩。故为第二长者斩。若然此当为第一义。古人反覆详释。而独不及此何也。传不言注不言疏不言。而必穷寻意虑之外。为不斩之證。亦辛苦矣。凡八岁以上皆为殇。既在童幼而死。恐不可以当第一之目。况殇服条公及大夫为嫡子之长殇大功。凡服降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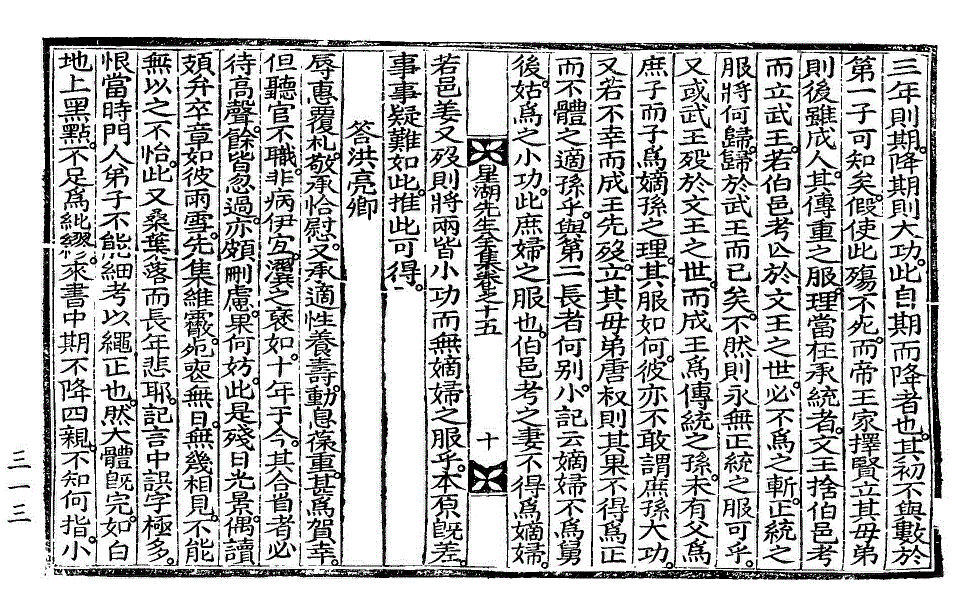 三年则期。降期则大功。此自期而降者也。其初不与数于第一子可知矣。假使此殇不死。而帝王家择贤立其母弟则后虽成人。其传重之服。理当在承统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若伯邑考亡于文王之世。必不为之斩。正统之服将何归。归于武王而已矣。不然则永无正统之服可乎。又或武王殁于文王之世。而成王为传统之孙。未有父为庶子而子为嫡孙之理。其服如何。彼亦不敢谓庶孙大功。又若不幸而成王先殁。立其母弟唐叔则其果不得为正而不体之适孙乎。与第二长者何别。小记云嫡妇不为舅后。姑为之小功。此庶妇之服也。伯邑考之妻不得为嫡妇。若邑姜又殁则将两皆小功而无嫡妇之服乎。本原既差。事事疑难如此。推此可得。
三年则期。降期则大功。此自期而降者也。其初不与数于第一子可知矣。假使此殇不死。而帝王家择贤立其母弟则后虽成人。其传重之服。理当在承统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若伯邑考亡于文王之世。必不为之斩。正统之服将何归。归于武王而已矣。不然则永无正统之服可乎。又或武王殁于文王之世。而成王为传统之孙。未有父为庶子而子为嫡孙之理。其服如何。彼亦不敢谓庶孙大功。又若不幸而成王先殁。立其母弟唐叔则其果不得为正而不体之适孙乎。与第二长者何别。小记云嫡妇不为舅后。姑为之小功。此庶妇之服也。伯邑考之妻不得为嫡妇。若邑姜又殁则将两皆小功而无嫡妇之服乎。本原既差。事事疑难如此。推此可得。答洪亮卿
辱惠覆札。敬承恰慰。又承适性养寿。动息葆重。甚为贺幸。但听官不职。非病伊宜。瀷之褎如。十年于今。其合省者必待高声。馀皆忽过。亦颇删虑。果何妨。此是残日光景。偶读頍弁卒章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不能无以之不怡。此又桑叶落而长年悲耶。记言中误字极多。恨当时门人弟子不能细考以绳正也。然大体既完。如白地上黑点。不足为纰缪。来书中期不降四亲。不知何指。小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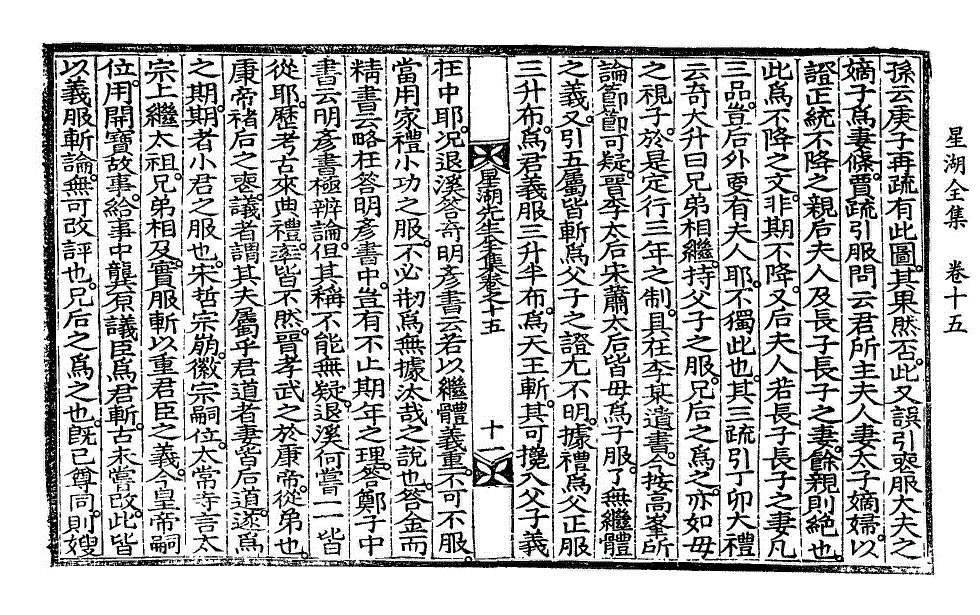 孙云庚子再疏有此图。其果然否。此又误引丧服大夫之嫡子为妻条。贾疏引服问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以證正统不降之亲后夫人及长子长子之妻。馀亲则绝也。此为不降之文。非期不降。又后夫人若长子长子之妻凡三品。岂后外更有夫人耶。不独此也。其三疏引丁卯大礼云奇大升曰兄弟相继。持父子之服。兄后之为之。亦如母之视子。于是定行三年之制。具在李某遗书。今按高峰所论节节可疑。晋李太后宋萧太后皆母为子服。了无继体之义。又引五属皆斩为父子之證尤不明。据礼为父正服三升布。为君义服三升半布。为天王斩。其可搀入父子义在中耶。况退溪答奇明彦书云若以继体义重。不可不服。当用家礼小功之服。不必刱为无据汰哉之说也。答金而精书云略在答明彦书中。岂有不止期年之理。答郑子中书云明彦书极辨论。但其称不能无疑。退溪何尝一一皆从耶。历考古来典礼。率皆不然。晋孝武之于康帝。从弟也。康帝褚后之丧。议者谓其夫属乎君道者妻皆后道。遂为之期。期者小君之服也。宋哲宗崩。徽宗嗣位。太常寺言太宗上继太祖。兄弟相及。实服斩以重君臣之义。今皇帝嗣位。用开宝故事。给事中龚原议臣为君斩。古未尝改。此皆以义服斩论。无可改评也。兄后之为之也。既已尊同。则嫂
孙云庚子再疏有此图。其果然否。此又误引丧服大夫之嫡子为妻条。贾疏引服问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以證正统不降之亲后夫人及长子长子之妻。馀亲则绝也。此为不降之文。非期不降。又后夫人若长子长子之妻凡三品。岂后外更有夫人耶。不独此也。其三疏引丁卯大礼云奇大升曰兄弟相继。持父子之服。兄后之为之。亦如母之视子。于是定行三年之制。具在李某遗书。今按高峰所论节节可疑。晋李太后宋萧太后皆母为子服。了无继体之义。又引五属皆斩为父子之證尤不明。据礼为父正服三升布。为君义服三升半布。为天王斩。其可搀入父子义在中耶。况退溪答奇明彦书云若以继体义重。不可不服。当用家礼小功之服。不必刱为无据汰哉之说也。答金而精书云略在答明彦书中。岂有不止期年之理。答郑子中书云明彦书极辨论。但其称不能无疑。退溪何尝一一皆从耶。历考古来典礼。率皆不然。晋孝武之于康帝。从弟也。康帝褚后之丧。议者谓其夫属乎君道者妻皆后道。遂为之期。期者小君之服也。宋哲宗崩。徽宗嗣位。太常寺言太宗上继太祖。兄弟相及。实服斩以重君臣之义。今皇帝嗣位。用开宝故事。给事中龚原议臣为君斩。古未尝改。此皆以义服斩论。无可改评也。兄后之为之也。既已尊同。则嫂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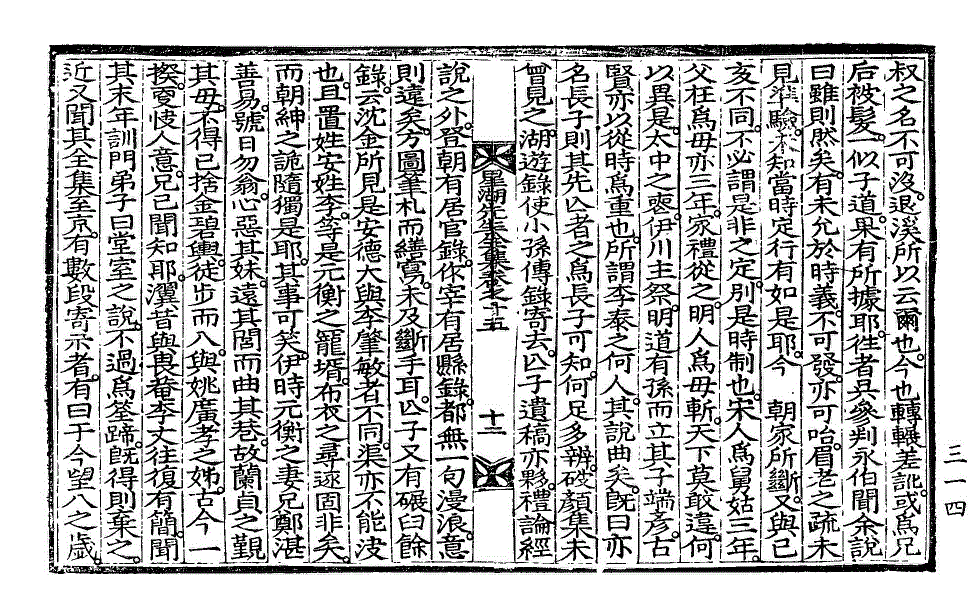 叔之名不可没。退溪所以云尔也。今也转辗差讹。或为兄后被发。一似子道。果有所据耶。往者吴参判永伯闻余说曰虽则然矣。有未允于时义。不可发。亦可咍。眉老之疏未见准验。未知当时定行有如是耶。今 朝家所断。又与己亥不同。不必谓是非之定。别是时制也。宋人为舅姑三年。父在为母亦三年。家礼从之。明人为母斩。天下莫敢违。何以异是。太中之丧。伊川主祭。明道有孙而立其子端彦。古贤亦以从时为重也。所谓李泰之何人。其说曲矣。既曰亦名长子则其先亡者之为长子可知。何足多辨。破颜集未曾见之。湖游录使小孙传录寄去。亡子遗稿亦夥。礼论经说之外。登朝有居官录。作宰有居县录。都无一句漫浪。意则远矣。方图笔札而缮写。未及断手耳。亡子又有碾臼馀录。云沈金所见是安德大与李肇敏者不同。渠亦不能决也。且置姓安姓李。等是元衡之宠婿。布衣之寻逐固非矣。而朝绅之诡随独是耶。其事可笑。伊时元衡之妻兄郑湛善易。号日勿翁。心恶其妹。远其闾而曲其巷。故兰贞之觐其母。不得已舍金碧舆。徒步而入。与姚广孝之姊。古今一揆。更快人意。兄已闻知耶。瀷昔与畏庵李丈往复有简。闻其末年训门弟子曰堂室之说。不过为筌蹄。既得则弃之。近又闻其全集至京。有数段寄示者。有曰于今望八之岁。
叔之名不可没。退溪所以云尔也。今也转辗差讹。或为兄后被发。一似子道。果有所据耶。往者吴参判永伯闻余说曰虽则然矣。有未允于时义。不可发。亦可咍。眉老之疏未见准验。未知当时定行有如是耶。今 朝家所断。又与己亥不同。不必谓是非之定。别是时制也。宋人为舅姑三年。父在为母亦三年。家礼从之。明人为母斩。天下莫敢违。何以异是。太中之丧。伊川主祭。明道有孙而立其子端彦。古贤亦以从时为重也。所谓李泰之何人。其说曲矣。既曰亦名长子则其先亡者之为长子可知。何足多辨。破颜集未曾见之。湖游录使小孙传录寄去。亡子遗稿亦夥。礼论经说之外。登朝有居官录。作宰有居县录。都无一句漫浪。意则远矣。方图笔札而缮写。未及断手耳。亡子又有碾臼馀录。云沈金所见是安德大与李肇敏者不同。渠亦不能决也。且置姓安姓李。等是元衡之宠婿。布衣之寻逐固非矣。而朝绅之诡随独是耶。其事可笑。伊时元衡之妻兄郑湛善易。号日勿翁。心恶其妹。远其闾而曲其巷。故兰贞之觐其母。不得已舍金碧舆。徒步而入。与姚广孝之姊。古今一揆。更快人意。兄已闻知耶。瀷昔与畏庵李丈往复有简。闻其末年训门弟子曰堂室之说。不过为筌蹄。既得则弃之。近又闻其全集至京。有数段寄示者。有曰于今望八之岁。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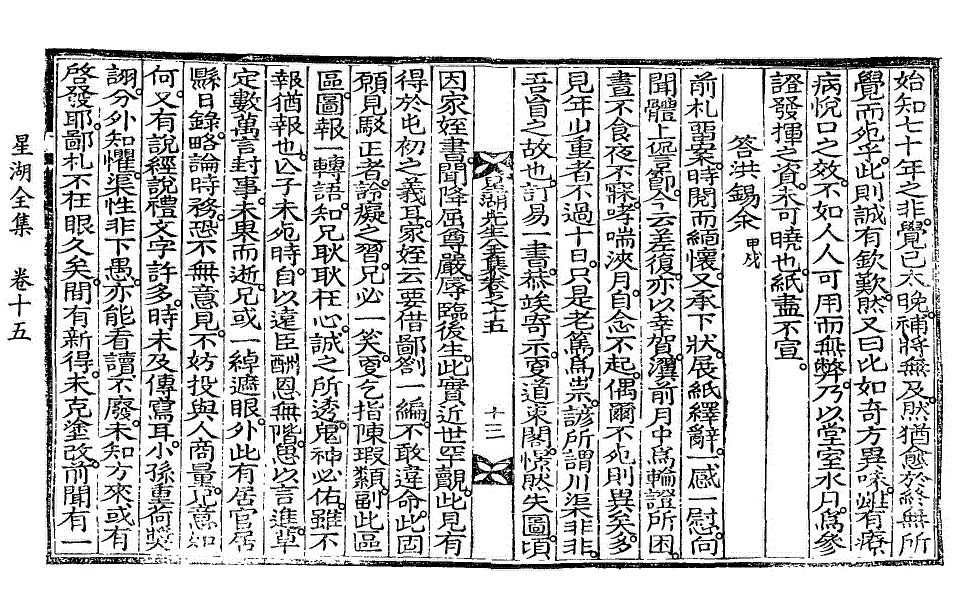 始知七十年之非。觉已太晚。补将无及。然犹愈于终无所觉而死乎。此则诚有钦叹。然又曰比如奇方异味。虽有疗病悦口之效。不如人人可用而无弊。乃以堂室水月。为参證发挥之资。未可晓也。纸尽不宣。
始知七十年之非。觉已太晚。补将无及。然犹愈于终无所觉而死乎。此则诚有钦叹。然又曰比如奇方异味。虽有疗病悦口之效。不如人人可用而无弊。乃以堂室水月。为参證发挥之资。未可晓也。纸尽不宣。答洪锡余(甲戌)
前札留案。时阅而缅怀。又承下状。展纸绎辞。一感一慰。向闻体上愆节。今云差复。亦以幸贺。瀷前月中为轮證所困。昼不食夜不寐。哮喘浃月。自念不起。偶尔不死则异矣。多见年少重者不过十日。只是老笃为祟。谚所谓川渠非非。吾盲之故也。订易一书。恭俟寄示。更道束阁。憬然失图。顷因家侄书。闻降屈尊严。辱临后生。此实近世罕觌。此见有得于屯初之义耳。家侄云要借鄙劄一编。不敢违命。此固愿见驳正者。詅痴之习。兄必一笑。更乞指陈瑕颣。副此区区。图报一转语。知兄耿耿在心。诚之所透。鬼神必佑。虽不报犹报也。亡子未死时。自以远臣酬恩无阶。思以言进。草定数万言封事。未果而逝。兄或一绰遮眼。外此有居官居县日录。略论时务。恐不无意见。不妨投与人商量。兄意如何。又有说经说礼文字许多。时未及传写耳。小孙重荷奖诩。分外知惧。渠性非下愚。亦能看读不废。未知方来或有启发耶。鄙札不在眼久矣。间有新得。未克涂改。前闻有一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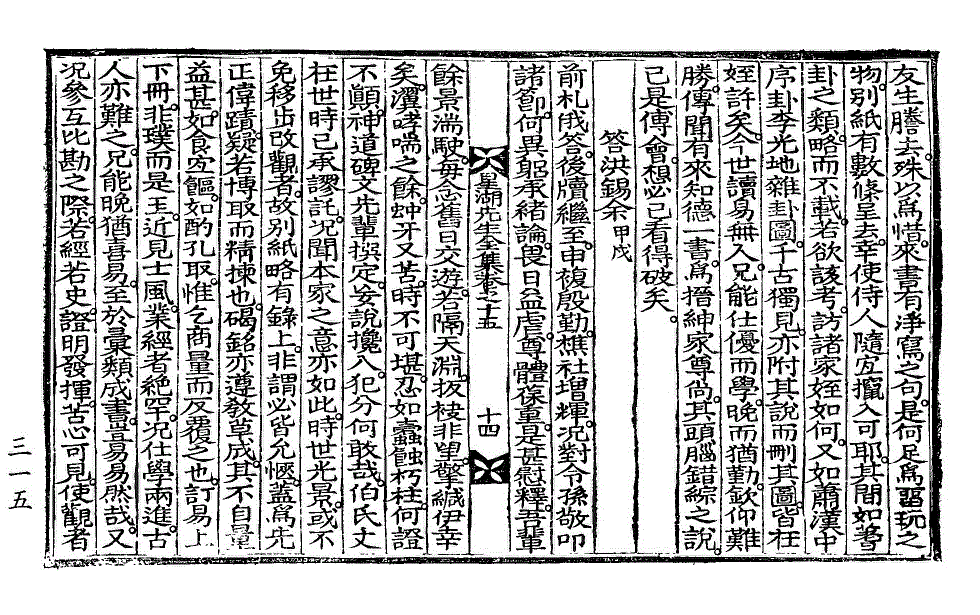 友生誊去。殊以为惜。来书有净写之句。是何足为留玩之物。别纸有数条呈去。幸使侍人随宜撺入可耶。其间如蓍卦之类。略而不载。若欲该考。访诸家侄如何。又如萧汉中序卦李光地杂卦图。千古独见。亦附其说而删其图。皆在侄许矣。今世读易无人。兄能仕优而学。晚而犹勤。钦仰难胜。传闻有来知德一书。为搢绅家尊尚。其头脑错综之说。已是傅会。想必已看得破矣。
友生誊去。殊以为惜。来书有净写之句。是何足为留玩之物。别纸有数条呈去。幸使侍人随宜撺入可耶。其间如蓍卦之类。略而不载。若欲该考。访诸家侄如何。又如萧汉中序卦李光地杂卦图。千古独见。亦附其说而删其图。皆在侄许矣。今世读易无人。兄能仕优而学。晚而犹勤。钦仰难胜。传闻有来知德一书。为搢绅家尊尚。其头脑错综之说。已是傅会。想必已看得破矣。答洪锡余(甲戌)
前札俄答。后牍继至。申复殷勤。樵社增辉。况对令孙敬叩诸节。何异躬承绪论。畏日益虐。尊体葆重。是甚慰释。吾辈馀景湍驶。每念旧日交游。若隔天渊。扳袂非望。擎缄伊幸矣。瀷哮喘之馀。蚛牙又苦。时不可堪。忍如蠹蚀朽柱。何證不颠。神道碑文先辈撰定。妄说搀入。犯分何敢哉。伯氏丈在世时已承谬托。况闻本家之意亦如此。时世光景。或不免移步改观者。故别纸略有录上。非谓必皆允惬。盖为先正伟迹。疑若博取而精拣也。碣铭亦遵教草成。其不自量益甚。如食宜饫。如酌孔取。惟乞商量而反覆之也。订易上下册。非璞而是玉。近见士风。业经者绝罕。况仕学两进。古人亦难之。兄能晚犹喜易。至于汇类成书。岂易易然哉。又况参互比勘之际。若经若史。證明发挥。苦心可见。使观者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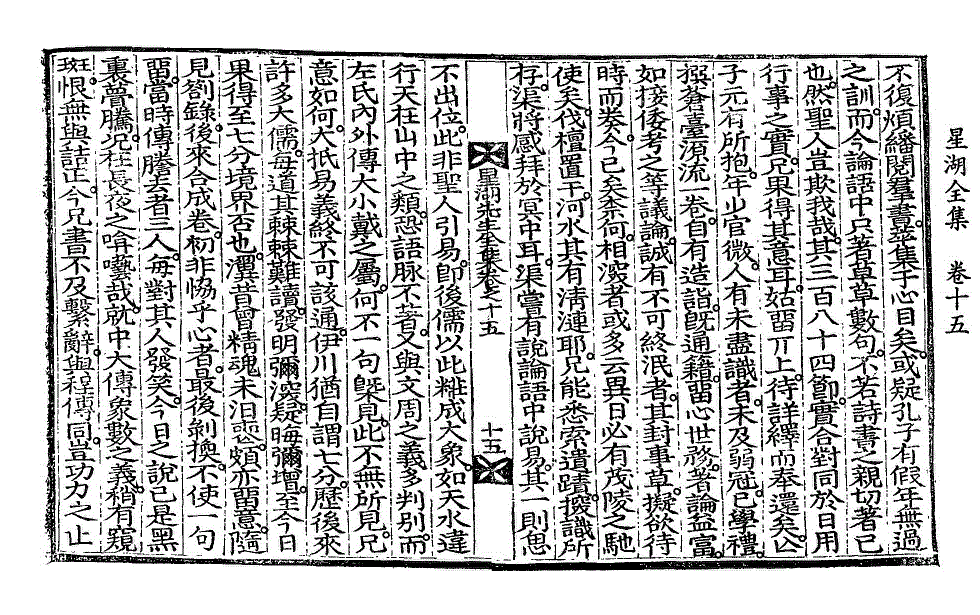 不复烦翻阅群书。萃集于心目矣。或疑孔子有假年无过之训。而今论语中只著草草数句。不若诗书之亲切著己也。然圣人岂欺我哉。其三百八十四节。实合对同于日用行事之实。兄果得其意耳。姑留丌上。待详绎而奉还矣。亡子元有所抱。年少官微。人有未尽识者。未及弱冠。已学礼。撰苍台源流一卷。自有造诣。既通籍。留心世务。著论益富。如接倭考之等议论。诚有不可终泯者。其封事草。拟欲待时而奏。今已矣柰何。相深者或多云异日必有茂陵之驰使矣。伐檀置干。河水其有清涟耶。兄能悉索遗迹。探识所存。渠将感拜于冥中耳。渠尝有说论语中说易。其一则思不出位。此非圣人引易。即后儒以此妆成大象。如天水违行天在山中之类。恐语脉不著。又与文周之义多判别。而左氏内外传大小戴之属。何不一句槩见。此不无所见。兄意如何。大抵易义终不可该通。伊川犹自谓七分。历后来许多大儒。每道其棘棘难读。发明弥深。疑晦弥增。至今日果得至七分境界否也。瀷昔曾精魂未汨丧。颇亦留意。随见劄录。后来合成卷。初非协乎心者。最后剥换。不使一句留。当时传誊去者三人。每对其人发笑。今日之说已是黑里瞢腾。况在长夜之啽呓哉。就中大传象数之义。稍有窥斑。恨无与诘正。今兄书不及系辞。与程传同。岂功力之止
不复烦翻阅群书。萃集于心目矣。或疑孔子有假年无过之训。而今论语中只著草草数句。不若诗书之亲切著己也。然圣人岂欺我哉。其三百八十四节。实合对同于日用行事之实。兄果得其意耳。姑留丌上。待详绎而奉还矣。亡子元有所抱。年少官微。人有未尽识者。未及弱冠。已学礼。撰苍台源流一卷。自有造诣。既通籍。留心世务。著论益富。如接倭考之等议论。诚有不可终泯者。其封事草。拟欲待时而奏。今已矣柰何。相深者或多云异日必有茂陵之驰使矣。伐檀置干。河水其有清涟耶。兄能悉索遗迹。探识所存。渠将感拜于冥中耳。渠尝有说论语中说易。其一则思不出位。此非圣人引易。即后儒以此妆成大象。如天水违行天在山中之类。恐语脉不著。又与文周之义多判别。而左氏内外传大小戴之属。何不一句槩见。此不无所见。兄意如何。大抵易义终不可该通。伊川犹自谓七分。历后来许多大儒。每道其棘棘难读。发明弥深。疑晦弥增。至今日果得至七分境界否也。瀷昔曾精魂未汨丧。颇亦留意。随见劄录。后来合成卷。初非协乎心者。最后剥换。不使一句留。当时传誊去者三人。每对其人发笑。今日之说已是黑里瞢腾。况在长夜之啽呓哉。就中大传象数之义。稍有窥斑。恨无与诘正。今兄书不及系辞。与程传同。岂功力之止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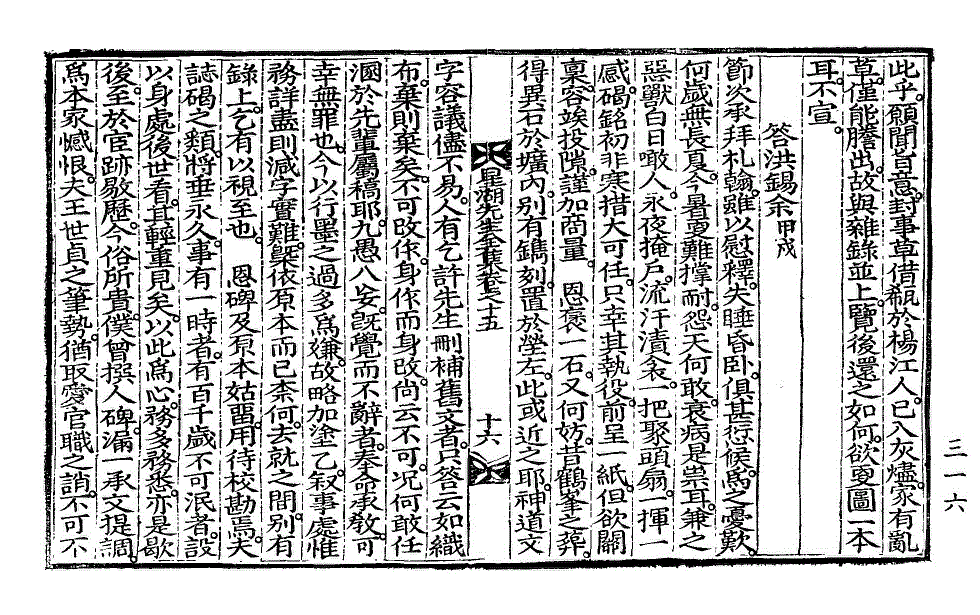 此乎。愿闻旨意。封事草借瓻于杨江人。已入灰烬。家有乱草。仅能誊出。故与杂录并上。览后还之如何。欲更图一本耳。不宣。
此乎。愿闻旨意。封事草借瓻于杨江人。已入灰烬。家有乱草。仅能誊出。故与杂录并上。览后还之如何。欲更图一本耳。不宣。答洪锡余(甲戌)
节次承拜札翰。虽以慰释。失睡昏卧。俱甚愆候。为之忧叹。何岁无长夏。今暑更难撑耐。怨天何敢。衰病是祟耳。兼之恶兽白日啖人。永夜掩户。流汗渍衾。一把聚头扇。一挥一感。碣铭初非寒措大可任。只幸其执役。前呈一纸。但欲关禀。容俟投隙。谨加商量。 恩褒一石。又何妨。昔鹤峰之葬。得异石于圹内。别有镌刻。置于茔左。此或近之耶。神道文字容议尽不易。人有乞许先生删补旧文者。只答云如织布。弃则弃矣。不可改作。身作而身改。尚云不可。况何敢任溷于先辈属稿耶。九愚八妄。既觉而不辞者。奉命承教。可幸无罪也。今以行墨之过多为嫌。故略加涂乙。叙事处惟务详尽则减字实难。槩依原本而已柰何。去就之间。别有录上。乞有以视至也。 恩碑及原本姑留。用待校勘焉。夫志碣之类。将垂永久。事有一时者。有百千岁不可泯者。设以身处后世看。其轻重见矣。以此为心。务多务悉。亦是歇后。至于宦迹扬历。今俗所贵。仆曾撰人碑。漏一承文提调。为本家憾恨。夫王世贞之笔势。犹取爱官职之诮。不可不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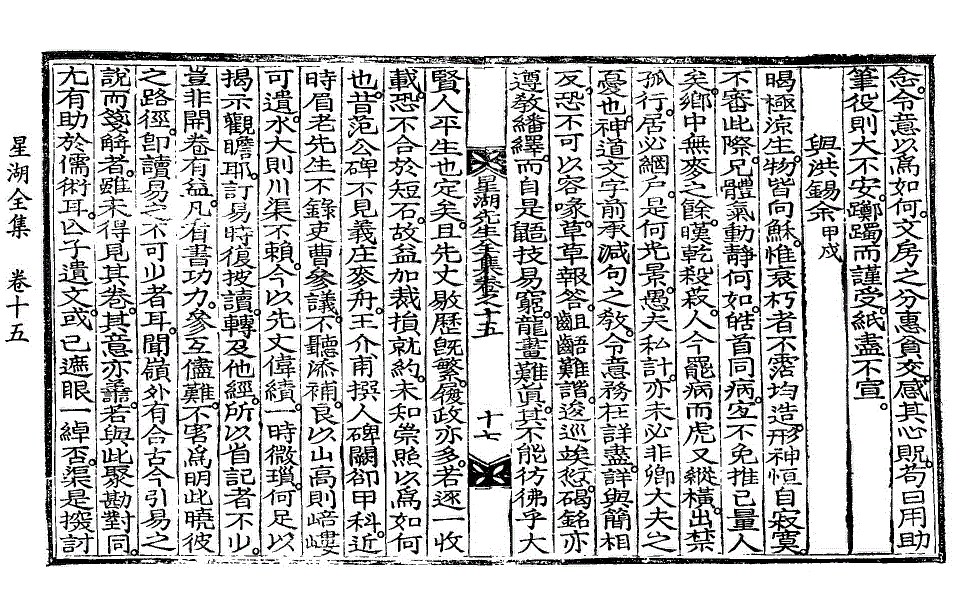 念。令意以为如何。文房之分惠贫交。感其心贶。苟曰用助笔役则大不安。踯躅而谨受。纸尽不宣。
念。令意以为如何。文房之分惠贫交。感其心贶。苟曰用助笔役则大不安。踯躅而谨受。纸尽不宣。与洪锡余(甲戌)
暍极凉生。物皆向稣。惟衰朽者不沾均造。形神恒自寂寞。不审此际。兄体气动静何如。皓首同病。宜不免推己量人矣。乡中无麦之馀。暵乾杀菽。人今罢病而虎又纵横。出禁孤行。居必网户。是何光景。愚夫私计。亦未必非卿大夫之忧也。神道文字前承减句之教。令意务在详尽。详与简相反。恐不可以容喙。草草报答。龃龉难谐。逡巡俟愆。碣铭亦遵教翻绎。而自是鼯技易穷。龙画难真。其不能彷佛乎大贤人平生也定矣。且先丈扬历既繁。履政亦多。若逐一收载。恐不合于短石。故益加裁损就约。未知崇照以为如何也。昔范公碑不见义庄麦舟。王介甫撰人碑阙却甲科。近时眉老先生不录吏曹参议。不听添补。良以山高则培嵝可遗。水大则川渠不赖。今以先丈伟绩。一时微琐。何足以揭示观瞻耶。订易时复披读。转及他经。所以省记者不少。岂非开卷有益。凡看书功力。参互尽难。不害为明此晓彼之路径。即读易之不可少者耳。闻岭外有合古今引易之说而笺解者。虽未得见其卷。其意亦善。若与此聚勘对同。尤有助于儒术耳。亡子遗文。或已遮眼一绰否。渠是探讨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7L 页
 于卷里。如谈龙肉而不知味者。其得与失。不能逃于真眼目。惟乞标纸题端。使观者有以去取之也。天下事非甲为则乙为。或者万一百十年后。有举措者。即亦渠之幸矣。前到两卷及碣草。裹在红襆谨呈。
于卷里。如谈龙肉而不知味者。其得与失。不能逃于真眼目。惟乞标纸题端。使观者有以去取之也。天下事非甲为则乙为。或者万一百十年后。有举措者。即亦渠之幸矣。前到两卷及碣草。裹在红襆谨呈。与洪锡余(甲戌)
新凉入郊。人思御裌。仰惟日用云为。与时俱宜。瀷向时轮證之后。益觉筋弛骸痿。只是块处幽嘿。以囱晖占其朝暮而已。订易时复翻阅。炤考经史。益见意味。实钦用力之深也。跋语闻命即图。惟惧醉吐文茵。搪探可讥。兄有不须促迫之语。以是窃揣摄养神气。更有遐远之想。如瀷之能老善丐者。但作一日活计。经宿以外。都未可保。何敢少须臾迁延。或不免于孤负耶。夫如是者。拙稿亦登棐几。投瓜报琼。不能不有望。两相传家。永以为好。即一事耳。亡子书草见借于杨根。已付炎火。将更谋一本。前去者览讫。还付车洞幸矣。贾生逸才。讵敢侔拟。其遇一主父为幸。丧茀滔滔。七日之得。盖寂寥无闻。儿生时与闻其意。贾亦言高罪也。系单于颈。伏中行而答背。非三表五饵之疏术可办。平城之后。中土创艾。文帝屈己。勉和息兵为上策。贾言所以不售也。故渠草中不犯 乘舆。不论一人臧否。惟就目下易识者说过。又恐伤烦。节略欠详。其能看得到此耶。东坡谓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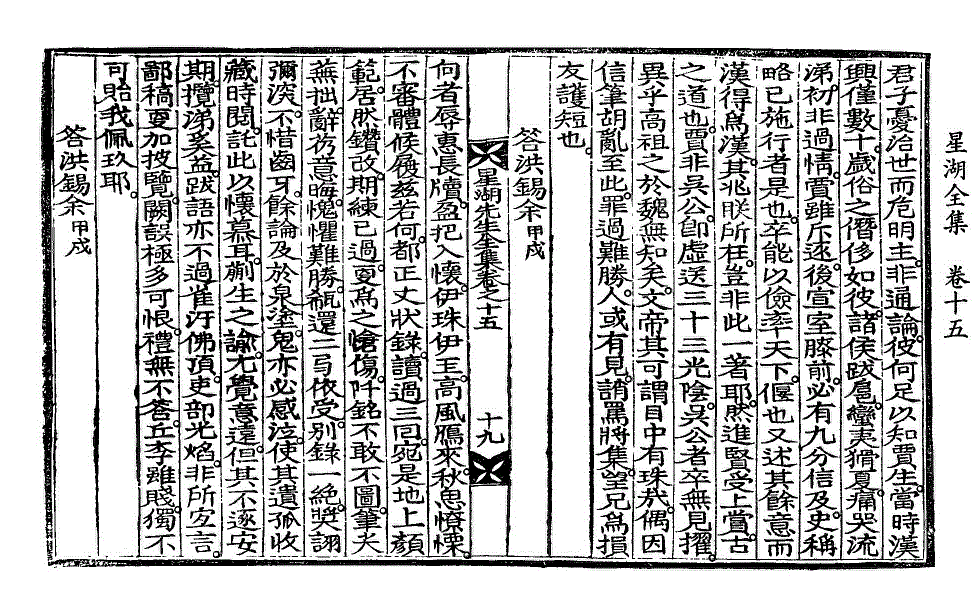 君子忧治世而危明主。非通论。彼何足以知贾生。当时汉兴仅数十。岁俗之僭侈如彼。诸侯跋扈。蛮夷猾夏。痛哭流涕。初非过情。贾虽斥逐。后宣室膝前。必有九分信及。史称略已施行者是也。卒能以俭率天下。偃也又述其馀意而汉得为汉。其兆朕所在。岂非此一著耶。然进贤受上赏。古之道也。贾非吴公。即虚送三十三光阴。吴公者卒无见擢。异乎高祖之于魏无知矣。文帝其可谓目中有珠哉。偶因信笔胡乱至此。罪过难胜。人或有见。诮骂将集。望兄为损友护短也。
君子忧治世而危明主。非通论。彼何足以知贾生。当时汉兴仅数十。岁俗之僭侈如彼。诸侯跋扈。蛮夷猾夏。痛哭流涕。初非过情。贾虽斥逐。后宣室膝前。必有九分信及。史称略已施行者是也。卒能以俭率天下。偃也又述其馀意而汉得为汉。其兆朕所在。岂非此一著耶。然进贤受上赏。古之道也。贾非吴公。即虚送三十三光阴。吴公者卒无见擢。异乎高祖之于魏无知矣。文帝其可谓目中有珠哉。偶因信笔胡乱至此。罪过难胜。人或有见。诮骂将集。望兄为损友护短也。答洪锡余(甲戌)
向者辱惠长牍。盈把入怀。伊珠伊玉。高风雁来。秋思憭慄。不审体候履玆若何。都正丈状录。读过三回。宛是地上颜范。居然钻改。期练已过。更为之怆伤。阡铭不敢不图。笔尖芜拙。辞芿意晦。愧惧难胜。瓻还二卷依受。别录一绝。奖诩弥深。不惜齿牙。馀论及于泉涂。鬼亦必感泣。使其遗孤收藏时阅。托此以怀慕耳。蒯生之谕。尤觉意远。但其不逐安期。揽涕奚益。跋语亦不过雀污佛顶。吏部光焰。非所宜言。鄙稿更加披览。阙误极多可恨。礼无不答。丘李虽贱。独不可贻我佩玖耶。
答洪锡余(甲戌)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8L 页
 宾雁传书。喜审尊履毖重。寄来一绝句。称量改换。垆锤之功。不遗馀力。殆所谓锱铢皆中也。令人佩服感泣。眷厚至此。不敢不扳和。语失停均。或涉太郎当。俟罪俟罪。
宾雁传书。喜审尊履毖重。寄来一绝句。称量改换。垆锤之功。不遗馀力。殆所谓锱铢皆中也。令人佩服感泣。眷厚至此。不敢不扳和。语失停均。或涉太郎当。俟罪俟罪。云自无心孰卷舒。知风端合付巢居。灵通不道幽明间。圯上何人重寄书。
终古名臣说仲舒。天人三策职思居。鲰生叵敢承前躅。一种嫠忧写在书。
答洪锡余(乙亥)
新年下状恭承。稽答是不独阙便。昏病神气。自不暇及。此罪过虽大。亦信閤下或不至深诃。不审月将再圆。冻解阡陌。随分从宦。日用万福。窃侧闻祇延先相公谥诰。瑞庆充闾。群情胥悦。恨不得陪下席而同此贺忭耳。此礼考诸 国朝五礼仪。无其说。恐据 国家延谥仪而酌损为之。亦念与追赠命帖。无甚判别。世俗极加张旺。伤财浩穰。故贫士不敢萌心。 命下而不得用者往往有之。可异。惟宜一二钜室先行。使人观而效之。未敢知兄能表微善图耶。顷札有无意邀宾之语。不免沾沾私喜矣。前赐诗筒。谨已咀嚼知其味矣。又闻兄能步履雅健。出入随意。不知何修而得此。瀷日计而觉其颓下。贫贱生涯。鬼亦慢以欺之耶。一笑。不宣。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9H 页
 答洪锡余(丁丑)
答洪锡余(丁丑)过询礼疑。尚不见 朝家节目。必有班示曲折。惟合谨守不越。何以问及于草间。若亿以谬见则礼所谓君丧不敢私服。服除而后殷祭者。即指兼有君亲之服者也。 国之内丧。于庶民无服。缟素而已。无五等之衰。恐与大夫士异例。如节日时食之类皆可废。而忌祭练祥等凶事。似无妨嫌。父服之内母之二祥皆行。何以异是。夫不可行则不行。单献无祝。更涉苟且。上墓之祭。退溪有素馔就庙之说。既是时节之飨。就庙何益。以素馔事神。尤非所闻。未知如何。朔参亦不过展诚之义。何可阙也。都在量以处之。岂可以穴蛰坯户之妄谈遽决耶。
答洪锡余(丁丑)
臣服斩于君。子服斩于父。皆服之至重。故孔子曰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注云大小二祥。不见有期服之丧。亦废私家三年之祭也。大夫服小君止于期。期比于三年有间矣。然此则经文可据。不敢臆说。今士大夫在君丧斩衰中。未闻一遵此制。五月之后皆行二祥。其有所见而然乎。未可知也。下文君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注殷谓朔望及荐新之奠。然则朝夕之祭依旧行于父丧。下文又云君未殡而臣有父母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19L 页
 丧。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室老及子孙行事。君虽未成服。而父母之丧反重。故舍君所而归哭父母。虽反于君所。犹归行私丧之殷事。室老子孙行事则未闻一日废朝夕之馈也。此又国君服斩之义。未闻小君服期亦如此也。又况据仪礼丧服。庶人为国君服止齐衰三月。其上文为旧君母妻。疏以为庶人无为小君之文。是恩浅。然则向之所论。都不过大夫之服君斩衰者。而其馀皆不在此例也。此文分明如此。未知别有他可證耶。问者愈多。故不得已注释以告之。宜并度事之轻重及人之贵贱则不待辨而明矣。又闻 因山既定。许民葬埋。葬则必虞。虞与练祥何别。既祭则三献单献何别。上山之祭。退溪有素馔就庙之训。废则当废。就庙何益。素馔尤无义也。鄙家凡系飨宴寒食重三之类皆废。朔日忌祭之类皆行矣。不祭犹可。祭而不变服何义。练而不练。祥而不缟可乎。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故惟士于公门。脱齐衰。私室变除。恐无禁令。如何。
丧。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室老及子孙行事。君虽未成服。而父母之丧反重。故舍君所而归哭父母。虽反于君所。犹归行私丧之殷事。室老子孙行事则未闻一日废朝夕之馈也。此又国君服斩之义。未闻小君服期亦如此也。又况据仪礼丧服。庶人为国君服止齐衰三月。其上文为旧君母妻。疏以为庶人无为小君之文。是恩浅。然则向之所论。都不过大夫之服君斩衰者。而其馀皆不在此例也。此文分明如此。未知别有他可證耶。问者愈多。故不得已注释以告之。宜并度事之轻重及人之贵贱则不待辨而明矣。又闻 因山既定。许民葬埋。葬则必虞。虞与练祥何别。既祭则三献单献何别。上山之祭。退溪有素馔就庙之训。废则当废。就庙何益。素馔尤无义也。鄙家凡系飨宴寒食重三之类皆废。朔日忌祭之类皆行矣。不祭犹可。祭而不变服何义。练而不练。祥而不缟可乎。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故惟士于公门。脱齐衰。私室变除。恐无禁令。如何。答洪锡余(戊寅)
料峭风寒。不审新春。颐寿万福。往者奉玩诗札。精神嘿会。唤起心况。也是残龄无上好事。耳中牛斗。即两翁相怜之病。而在瀷有甚焉。脑转聒乱。或类啼哭。岂吉祥善事耶。在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0H 页
 京游从。只有兄与圣文二老。俄闻文丈又作泉下人。比如晓星稍稍没去必悠然。惟存者增伤。惠章欲有扳和。形躯寂寞。思搜不得。留俟日长而图之耳。令孙闻颇才华。能劬学进修否。吾辈所可勉。不过诲尔式谷。顷得天安少友札。亦觉彬彬。尊门后进。深有期望。为之嘉叹。启心蹇留京里。蝉腹龟肠。居大不易。将何以撑度。毫役甚艰。不能折简问讯。如或在侍。幸为导达焉。闻有和汉名数一书至国。日本人所撰。极有可观。或有可求处耶。如使入把。幸传与鄙人看。缕息将绝。结习犹存。自笑自憎。此意亦付嘱于圣源大夫。不宣。
京游从。只有兄与圣文二老。俄闻文丈又作泉下人。比如晓星稍稍没去必悠然。惟存者增伤。惠章欲有扳和。形躯寂寞。思搜不得。留俟日长而图之耳。令孙闻颇才华。能劬学进修否。吾辈所可勉。不过诲尔式谷。顷得天安少友札。亦觉彬彬。尊门后进。深有期望。为之嘉叹。启心蹇留京里。蝉腹龟肠。居大不易。将何以撑度。毫役甚艰。不能折简问讯。如或在侍。幸为导达焉。闻有和汉名数一书至国。日本人所撰。极有可观。或有可求处耶。如使入把。幸传与鄙人看。缕息将绝。结习犹存。自笑自憎。此意亦付嘱于圣源大夫。不宣。答洪锡余(戊寅)
俄自柳村转寄书到。仰审春暮。体气与时舒泰。吾辈残龄。旬月安过消息。煞是难得。瀷五官都秏。两车各留一牙。仅嚼软饭。支度缕命。近时益觉酸动。不堪噍食。万事无不可通变者。惟此没柰何矣。和汉一卷。尽觉无用。顷有一朋云有可观故必要圣源令公求见。果然见不如闻矣。向奉诗笺。病昏未及扳和。佩玖之贻。丘李阙报则罪也。今见圣源大夫之寄章。省愆补过。录在尾端。必惠我一笑耳。不宣。
答洪锡余(庚辰)
问札经旬始到。虽以慰释。亦不审信后起居日间尊候更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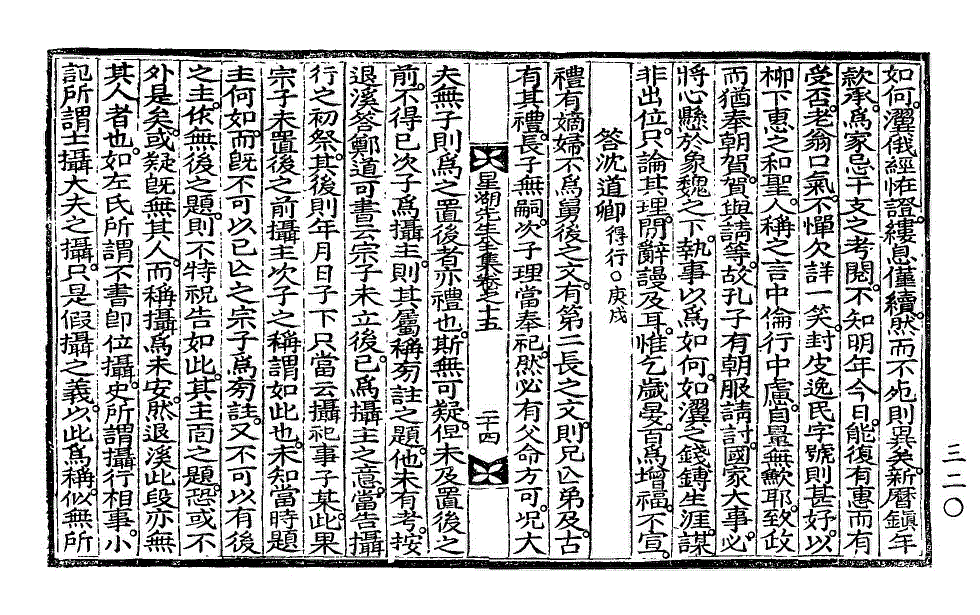 如何。瀷俄经怪證。缕息仅续。然而不死则异矣。新历镇年款承。为家忌干支之考阅。不知明年今日。能复有惠而有受否。老翁口气。不惮欠详一笑。封皮逸民字号则甚好。以柳下惠之和圣。人称之言中伦行中虑。自量无歉耶。致政而犹奉朝贺。贺与请等。故孔子有朝服请讨。国家大事。必将心悬于象魏之下。执事以为如何。如瀷之钱镈生涯。谋非出位。只论其理。閒辞谩及耳。惟乞岁晏。百为增福。不宣。
如何。瀷俄经怪證。缕息仅续。然而不死则异矣。新历镇年款承。为家忌干支之考阅。不知明年今日。能复有惠而有受否。老翁口气。不惮欠详一笑。封皮逸民字号则甚好。以柳下惠之和圣。人称之言中伦行中虑。自量无歉耶。致政而犹奉朝贺。贺与请等。故孔子有朝服请讨。国家大事。必将心悬于象魏之下。执事以为如何。如瀷之钱镈生涯。谋非出位。只论其理。閒辞谩及耳。惟乞岁晏。百为增福。不宣。答沈道卿(得行○庚戌)
礼有嫡妇不为舅后之文。有第二长之文。则兄亡弟及。古有其礼。长子无嗣。次子理当奉祀。然必有父命方可。况大夫无子则为之置后者亦礼也。斯无可疑。但未及置后之前。不得已次子为摄主。则其属称旁注之题。他未有考。按退溪答郑道可书云宗子未立后。己为摄主之意。当告摄行之初祭。其后则年月日子下只当云摄祀事子某。此果宗子未置后之前摄主次子之称谓如此也。未知当时题主何如。而既不可以已亡之宗子为旁注。又不可以有后之主。作无后之题。则不特祝告如此。其主面之题。恐或不外是矣。或疑既无其人。而称摄为未安。然退溪此段亦无其人者也。如左氏所谓不书即位摄。史所谓摄行相事。小记所谓士摄大夫之摄。只是假摄之义。以此为称。似无所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1H 页
 嫌。然则据称名不言孝之例题旁注云子某摄祀。抑或近之。而又不必言祀事也。盖礼摄大夫之事。只曰摄大夫。则可以推矣。至祝告亦但云摄祀子某。未知如何。
嫌。然则据称名不言孝之例题旁注云子某摄祀。抑或近之。而又不必言祀事也。盖礼摄大夫之事。只曰摄大夫。则可以推矣。至祝告亦但云摄祀子某。未知如何。素馔之祭。未之前闻。丧内遇祖先忌日者。退溪答琴闻远云难以臆决。答金敦叙云神道有异于生人。用肉无妨。盖始疑而终断也。虽与此少异。忌日亦一日之丧。而古人以丧礼处之。亦可以旁推矣。若因其父母之丧而不忍荐之以非礼之美味。则酒馔菜果。等是为可废。而酒比于肉。其失尤大也。且居丧之礼。病则许酒肉矣。病而至于亡矣。其庋阁馀奠可忍废耶。顷阅文宪公年谱中有论此极明。乃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可以取考。
祔祭虽曰吉事。既是异宫。今于本生丧之葬前。疑若无可废之义。然其于废之无害者。权以暂停。未为不可。殷人练而祔。而孔子善之。至小祥明日乃行。恐似得之。然卒哭时须告权退之意。至小祥祝。先告跻祔如卒哭之祝。方为宛转。
答沈道卿(甲子)
覆札恭承恰慰。况凭审新年舒晷。尊体履端万重。尤不胜贺幸。瀷呻病跨岁。坏户未启。嘿念自此不复为充完人矣。许先生年谱向奉校阅之教。犹不觉剞劂期近。故不免束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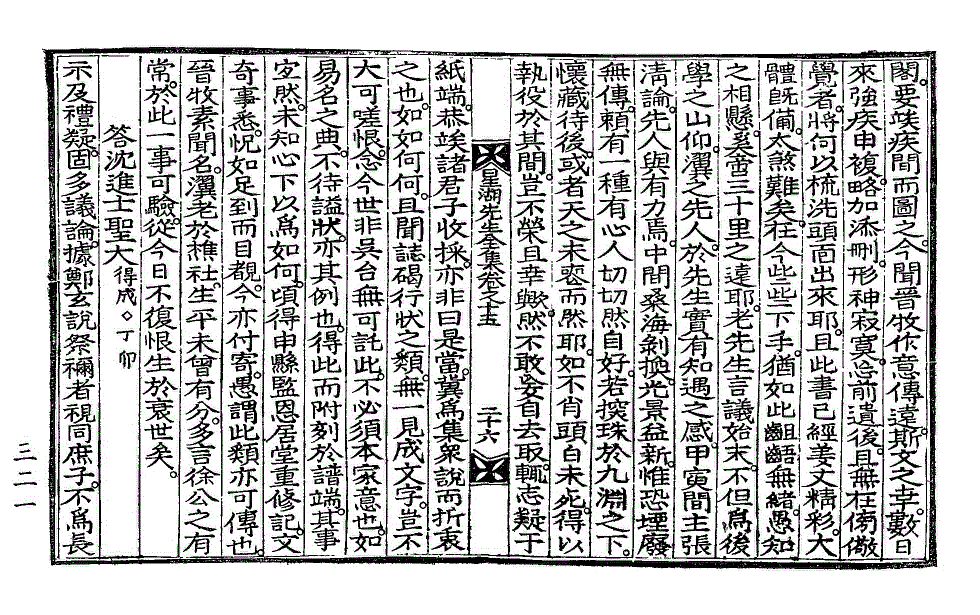 阁。要俟疾间而图之。今闻晋牧作意传远。斯文之幸。数日来强疾申复。略加添删。形神寂寞。忘前遗后。且无在傍儆觉者。将何以梳洗头面出来耶。且此书已经姜丈精彩。大体既备。太煞难矣。在今些些下手。犹如此龃龉无绪。愚知之相悬。奚啻三十里之远耶。老先生言议始末。不但为后学之山仰。瀷之先人。于先生实有知遇之感。甲寅间主张清论。先人与有力焉。中间桑海剥换。光景益新。惟恐堙废无传。赖有一种有心人切切然自好。若探珠于九渊之下。怀藏待后。或者天之未丧而然耶。如不肖头白未死。得以执役于其间。岂不荣且幸欤。然不敢妄自去取。辄志疑于纸端。恭俟诸君子收采。亦非曰是当。冀为集众说而折衷之也。如如何何。且闻志碣行状之类。无一见成文字。岂不大可嗟恨。念今世非吴台无可托此。不必须本家意也。如易名之典。不待谥状。亦其例也。得此而附刻于谱端。其事宜然。未知心下以为如何。顷得申县监恩居堂重修记。文奇事悉。恍如足到而目睹。今亦付寄。愚谓此类亦可传也。晋牧素闻名。瀷老于樵社。生平未曾有分。多言徐公之有常。于此一事可验。从今日不复恨生于衰世矣。
阁。要俟疾间而图之。今闻晋牧作意传远。斯文之幸。数日来强疾申复。略加添删。形神寂寞。忘前遗后。且无在傍儆觉者。将何以梳洗头面出来耶。且此书已经姜丈精彩。大体既备。太煞难矣。在今些些下手。犹如此龃龉无绪。愚知之相悬。奚啻三十里之远耶。老先生言议始末。不但为后学之山仰。瀷之先人。于先生实有知遇之感。甲寅间主张清论。先人与有力焉。中间桑海剥换。光景益新。惟恐堙废无传。赖有一种有心人切切然自好。若探珠于九渊之下。怀藏待后。或者天之未丧而然耶。如不肖头白未死。得以执役于其间。岂不荣且幸欤。然不敢妄自去取。辄志疑于纸端。恭俟诸君子收采。亦非曰是当。冀为集众说而折衷之也。如如何何。且闻志碣行状之类。无一见成文字。岂不大可嗟恨。念今世非吴台无可托此。不必须本家意也。如易名之典。不待谥状。亦其例也。得此而附刻于谱端。其事宜然。未知心下以为如何。顷得申县监恩居堂重修记。文奇事悉。恍如足到而目睹。今亦付寄。愚谓此类亦可传也。晋牧素闻名。瀷老于樵社。生平未曾有分。多言徐公之有常。于此一事可验。从今日不复恨生于衰世矣。答沈进士圣大(得成○丁卯)
示及礼疑。固多议论。据郑玄说祭祢者视同庶子。不为长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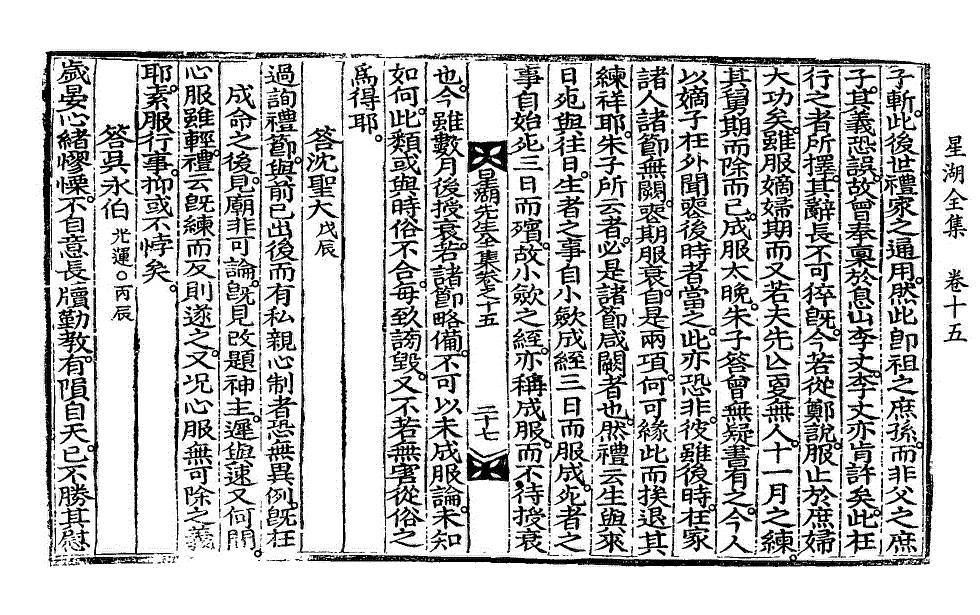 子斩。此后世礼家之通用。然此即祖之庶孙。而非父之庶子。其义恐误。故曾奉禀于息山李丈。李丈亦肯许矣。此在行之者所择。其辞长不可猝既。今若从郑说。服止于庶妇大功矣。虽服嫡妇期而又若夫先亡更无人。十一月之练。其舅期而除而已。成服太晚。朱子答曾无疑书有之。今人以嫡子在外闻丧后时者当之。此亦恐非。彼虽后时。在家诸人诸节无阙。丧期服衰。自是两项。何可缘此而挨退其练祥耶。朱子所云者。必是诸节咸阙者也。然礼云生与来日死与往日。生者之事自小敛成绖三日而服成。死者之事自始死三日而殡。故小敛之绖。亦称成服。而不待授衰也。今虽数月后授衰。若诸节略备。不可以未成服论。未知如何。此类或与时俗不合。每致谤毁。又不若无害从俗之为得耶。
子斩。此后世礼家之通用。然此即祖之庶孙。而非父之庶子。其义恐误。故曾奉禀于息山李丈。李丈亦肯许矣。此在行之者所择。其辞长不可猝既。今若从郑说。服止于庶妇大功矣。虽服嫡妇期而又若夫先亡更无人。十一月之练。其舅期而除而已。成服太晚。朱子答曾无疑书有之。今人以嫡子在外闻丧后时者当之。此亦恐非。彼虽后时。在家诸人诸节无阙。丧期服衰。自是两项。何可缘此而挨退其练祥耶。朱子所云者。必是诸节咸阙者也。然礼云生与来日死与往日。生者之事自小敛成绖三日而服成。死者之事自始死三日而殡。故小敛之绖。亦称成服。而不待授衰也。今虽数月后授衰。若诸节略备。不可以未成服论。未知如何。此类或与时俗不合。每致谤毁。又不若无害从俗之为得耶。答沈圣大(戊辰)
过询礼节。与前已出后而有私亲心制者恐无异例。既在 成命之后。见庙非可论。既见改题神主。迟与速又何间。心服虽轻。礼云既练而反则遂之。又况心服无可除之义耶。素服行事。抑或不悖矣。
答吴永伯(光运○丙辰)
岁晏心绪憀慄。不自意长牍勤教。有陨自天。已不胜其慰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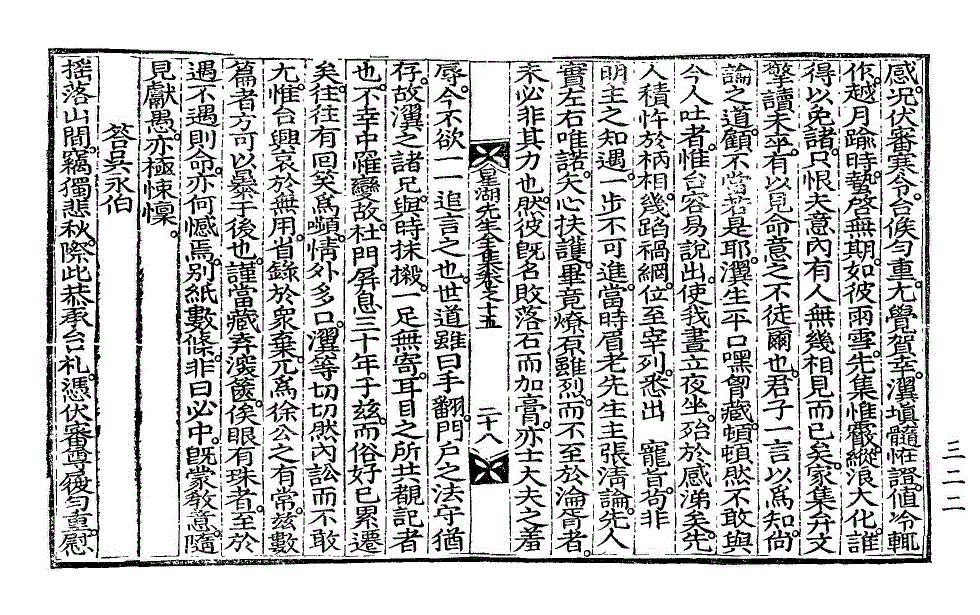 感。况伏审寒令。台候匀重。尤觉贺幸。瀷填髓怪證。值冷辄作。越月踰时。蛰启无期。如彼雨雪。先集惟霰。纵浪大化。谁得以免诸。只恨夫意内有人无几相见而已矣。家集弁文擎读未卒。有以见命意之不徒尔也。君子一言以为知。尚论之道。顾不当若是耶。瀷生平口嘿胸藏。顿顿然不敢与今人吐者。惟台容易说出。使我昼立夜坐。殆于感涕矣。先人积忤于柄相。几蹈祸网。位至宰列。悉出 宠旨。苟非 明主之知遇。一步不可进。当时眉老先生主张清论。先人实左右唯诺。矢心扶护。毕竟燎原虽烈。而不至于沦胥者。未必非其力也。然彼既名败落石而加膏。亦士大夫之羞辱。今不欲一一追言之也。世道虽曰手翻。门户之法守犹存。故瀷之诸兄。与时抹摋。一足无寄。耳目之所共睹记者也。不幸中罹变故。杜门屏息三十年于玆。而俗好已累迁矣。往往有回笑为嚬。情外多口。瀷等切切然内讼而不敢尤。惟台兴哀于无用。省录于众弃。兀为徐公之有常。玆数篇者方可以㬥于后也。谨当藏弆深箧。俟眼有珠者。至于遇不遇则命。亦何憾焉。别纸数条。非曰必中。既蒙教意。随见献愚。亦极悚懔。
感。况伏审寒令。台候匀重。尤觉贺幸。瀷填髓怪證。值冷辄作。越月踰时。蛰启无期。如彼雨雪。先集惟霰。纵浪大化。谁得以免诸。只恨夫意内有人无几相见而已矣。家集弁文擎读未卒。有以见命意之不徒尔也。君子一言以为知。尚论之道。顾不当若是耶。瀷生平口嘿胸藏。顿顿然不敢与今人吐者。惟台容易说出。使我昼立夜坐。殆于感涕矣。先人积忤于柄相。几蹈祸网。位至宰列。悉出 宠旨。苟非 明主之知遇。一步不可进。当时眉老先生主张清论。先人实左右唯诺。矢心扶护。毕竟燎原虽烈。而不至于沦胥者。未必非其力也。然彼既名败落石而加膏。亦士大夫之羞辱。今不欲一一追言之也。世道虽曰手翻。门户之法守犹存。故瀷之诸兄。与时抹摋。一足无寄。耳目之所共睹记者也。不幸中罹变故。杜门屏息三十年于玆。而俗好已累迁矣。往往有回笑为嚬。情外多口。瀷等切切然内讼而不敢尤。惟台兴哀于无用。省录于众弃。兀为徐公之有常。玆数篇者方可以㬥于后也。谨当藏弆深箧。俟眼有珠者。至于遇不遇则命。亦何憾焉。别纸数条。非曰必中。既蒙教意。随见献愚。亦极悚懔。答吴永伯
摇落山间。窃独悲秋。际此恭承台札。凭伏审尊履匀重。慰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3H 页
 释难胜。家集二序。又蒙墨洒卷首。荣宠倍增。朝晷夜灯。忍涕庄诵。从今日知吾父吾兄心者。惟閤下在耳。桑海屡换。睹记渐堙。而谁知之。又向谁语哉。自见此文字。如闻世外笙箫。惝恍若疑。近因儿子做官。厚被 国恩。使四十年杜门畏影之踪。能轩眉作人世上语。意者精神嘿会。有开必先耶。此殆难以言语形容说出。台必嘿有以谅之矣。瀷自夏秋入冬。困于背痤。恒觉七分泉下意思。迹阻京里。无由踵门款谢。徒怀罪悚。
释难胜。家集二序。又蒙墨洒卷首。荣宠倍增。朝晷夜灯。忍涕庄诵。从今日知吾父吾兄心者。惟閤下在耳。桑海屡换。睹记渐堙。而谁知之。又向谁语哉。自见此文字。如闻世外笙箫。惝恍若疑。近因儿子做官。厚被 国恩。使四十年杜门畏影之踪。能轩眉作人世上语。意者精神嘿会。有开必先耶。此殆难以言语形容说出。台必嘿有以谅之矣。瀷自夏秋入冬。困于背痤。恒觉七分泉下意思。迹阻京里。无由踵门款谢。徒怀罪悚。答姜子淳(朴)
家礼三加巾服。多与古不同。其四䙆襕衫之类。只是从时也。既非古制。又违俗尚。则略加通变。斯恐为善学家礼也。示谕数条。槩与鄙意合。礼曰天下无生而贵者。天子之元子犹士也。无官者恐不得通用大夫之礼也。婚礼虽曰摄盛。士乘大夫墨车。大夫乘夏缦。卿乘夏篆而已。今之庶人用公卿之服者。于礼不合矣。故家礼分明著有官无官之别。不可违也。初加深衣幅巾。无可更议。按礼始加缁布。尚古也。冠而废之。非时用也。再加以下。容有从时之义也。所谓帽子。不详何制。语类云前辈士大夫家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即家礼再加之服也。又云温公冠礼先裹巾。次裹帽。此皆时俗之制。而因以为礼也。意者帽子者。以皂纱裹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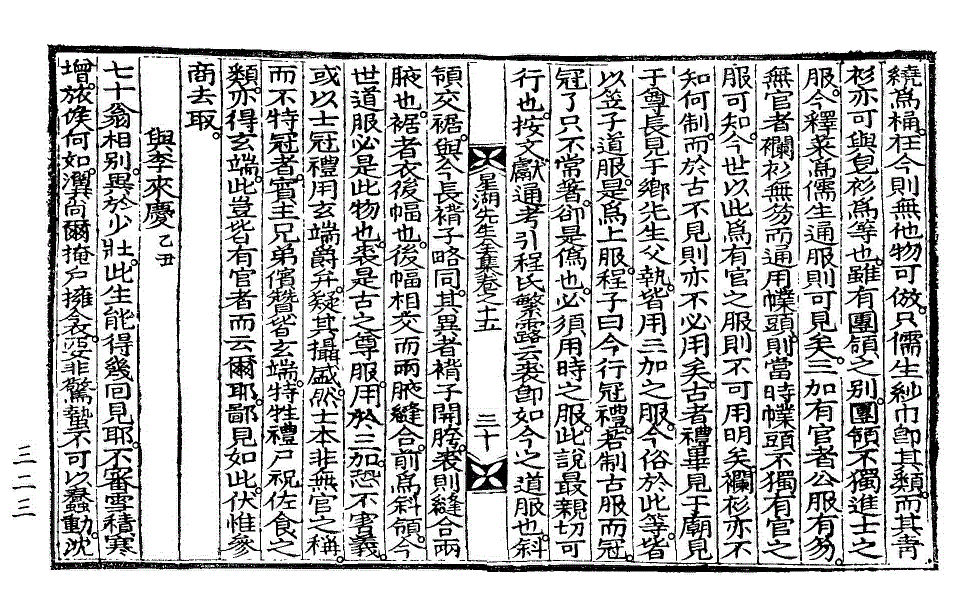 绕为桶。在今则无他物可仿。只儒生纱巾即其类。而其青衫亦可与皂衫为等也。虽有团领之别。团领不独进士之服。今释菜为儒生通服则可见矣。三加有官者公服有笏。无官者襕衫无笏而通用幞头。则当时幞头不独有官之服可知。今世以此为有官之服则不可用明矣。襕衫亦不知何制。而于古不见则亦不必用矣。古者礼毕见于庙见于尊长见于乡先生父执。皆用三加之服。今俗于此等。皆以笠子道服。是为上服。程子曰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只不常著。却是伪也。必须用时之服。此说最亲切可行也。按文献通考引程氏繁露云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领交裾。与今长褙子略同。其异者褙子开胯。裘则缝合两腋也。裾者衣后幅也。后幅相交而两腋缝合。前为斜领。今世道服必是此物也。裘是古之尊服。用于三加。恐不害义。或以士冠礼用玄端爵弁。疑其摄盛。然士本非无官之称。而不特冠者。宾主兄弟傧赞皆玄端。特牲礼尸祝佐食之类。亦得玄端。此岂皆有官者而云尔耶。鄙见如此。伏惟参商去取。
绕为桶。在今则无他物可仿。只儒生纱巾即其类。而其青衫亦可与皂衫为等也。虽有团领之别。团领不独进士之服。今释菜为儒生通服则可见矣。三加有官者公服有笏。无官者襕衫无笏而通用幞头。则当时幞头不独有官之服可知。今世以此为有官之服则不可用明矣。襕衫亦不知何制。而于古不见则亦不必用矣。古者礼毕见于庙见于尊长见于乡先生父执。皆用三加之服。今俗于此等。皆以笠子道服。是为上服。程子曰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只不常著。却是伪也。必须用时之服。此说最亲切可行也。按文献通考引程氏繁露云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领交裾。与今长褙子略同。其异者褙子开胯。裘则缝合两腋也。裾者衣后幅也。后幅相交而两腋缝合。前为斜领。今世道服必是此物也。裘是古之尊服。用于三加。恐不害义。或以士冠礼用玄端爵弁。疑其摄盛。然士本非无官之称。而不特冠者。宾主兄弟傧赞皆玄端。特牲礼尸祝佐食之类。亦得玄端。此岂皆有官者而云尔耶。鄙见如此。伏惟参商去取。与李来庆(乙丑)
七十翁相别。异于少壮。此生能得几回见耶。不审雪积寒增。旅候何如。瀷尚尔掩户拥衾。要非惊蛰不可以蠢动。沈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4H 页
 存中笔谈仔细阅过。槩是傅会。所谓名可易序不可易者虽若近之。其祀天祭地享先之乐。节节异例。古制必不如是穿凿。且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夹钟者亦未然。九变八变。则合矣。至圜钟六变。以林钟南吕夷则无清宫不用。若然其一变无射。再变仲吕。又何以无清宫而数之乎。黄钟之一变三变八变。函钟之再变七变。独数此三律何也。况只存四清声。古未必有是也。但亥卯未为三钟。巳酉丑为三吕。此最有理。其奏歌用六合。其变则用地支之数。而此又用三合。皆术家之所祖也。别来重考大司乐二条。时有管窥。别纸录呈。幸有以反覆之也。家儿亦曾思未及此。脱直必过谒。须与之商量也。然此不过老生口业。后来太常轩悬。何尝有此耶。枯项垂死而嘐嘐之志尚有未尽泯者一笑。今俗有抛毬乐者。寻常不晓其义。笔谈中有之。能省觉耶此从胜国时已有之。胜国大晟之类悉自中土传来故也。
存中笔谈仔细阅过。槩是傅会。所谓名可易序不可易者虽若近之。其祀天祭地享先之乐。节节异例。古制必不如是穿凿。且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夹钟者亦未然。九变八变。则合矣。至圜钟六变。以林钟南吕夷则无清宫不用。若然其一变无射。再变仲吕。又何以无清宫而数之乎。黄钟之一变三变八变。函钟之再变七变。独数此三律何也。况只存四清声。古未必有是也。但亥卯未为三钟。巳酉丑为三吕。此最有理。其奏歌用六合。其变则用地支之数。而此又用三合。皆术家之所祖也。别来重考大司乐二条。时有管窥。别纸录呈。幸有以反覆之也。家儿亦曾思未及此。脱直必过谒。须与之商量也。然此不过老生口业。后来太常轩悬。何尝有此耶。枯项垂死而嘐嘐之志尚有未尽泯者一笑。今俗有抛毬乐者。寻常不晓其义。笔谈中有之。能省觉耶此从胜国时已有之。胜国大晟之类悉自中土传来故也。答金掌令(光运)
谨拜承七月二十二日下状。伏以尊体万福为慰释。过询礼节。极是难处。曾闻亲知数家有此事。瀷幸与有闻知矣。虽未决其去就果如何。而执事所处与之略符。盖独子后大宗。以其次子还承本生祀。此不但诸葛事有是。通典田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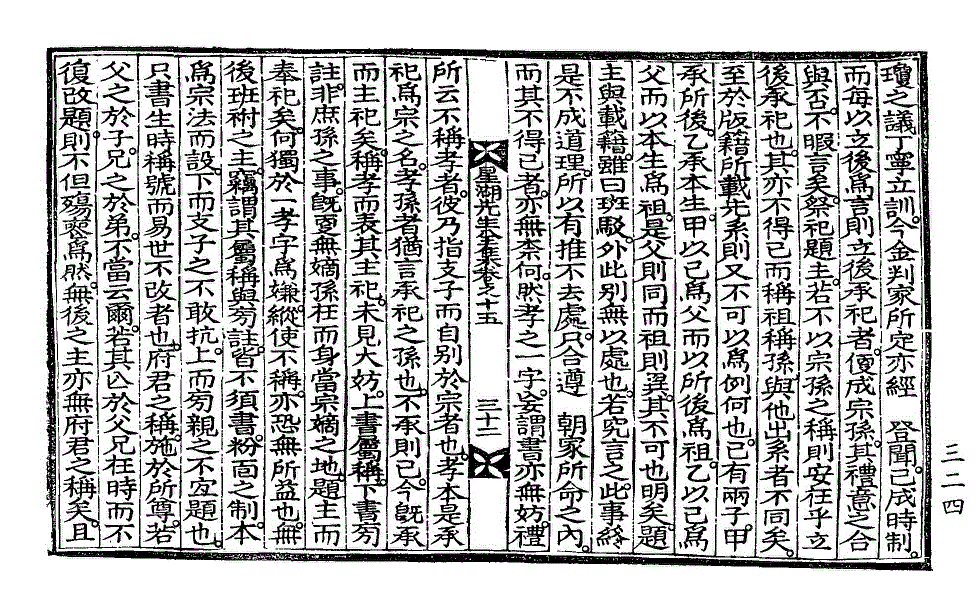 琼之议丁宁立训。今金判家所定亦经 登闻。已成时制。而每以立后为言则立后承祀者。便成宗孙。其礼意之合与否。不暇言矣。祭祀题主。若不以宗孙之称则安在乎立后承祀也。其亦不得已而称祖称孙。与他出系者不同矣。至于版籍所载先系则又不可以为例何也。己有两子。甲承所后。乙承本生。甲以己为父而以所后为祖。乙以己为父而以本生为祖。是父则同而祖则异。其不可也明矣。题主与载籍。虽曰斑驳。外此别无以处也。若究言之。此事终是不成道理。所以有推不去处。只合遵 朝家所命之内。而其不得已者。亦无柰何。然孝之一字。妄谓书亦无妨。礼所云不称孝者。彼乃指支子而自别于宗者也。孝本是承祀为宗之名。孝孙者犹言承祀之孙也。不承则已。今既承而主祀矣。称孝而表其主祀。未见大妨。上书属称。下书旁注。非庶孙之事。既更无嫡孙在而身当宗嫡之地。题主而奉祀矣。何独于一孝字为嫌。纵使不称。亦恐无所益也。无后班祔之主。窃谓其属称与旁注。皆不须书。粉面之制。本为宗法而设。下而支子之不敢抗。上而旁亲之不宜题也。只书生时称号而易世不改者也。府君之称。施于所尊。若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不当云尔。若其亡于父兄在时而不复改题。则不但殇丧为然。无后之主亦无府君之称矣。且
琼之议丁宁立训。今金判家所定亦经 登闻。已成时制。而每以立后为言则立后承祀者。便成宗孙。其礼意之合与否。不暇言矣。祭祀题主。若不以宗孙之称则安在乎立后承祀也。其亦不得已而称祖称孙。与他出系者不同矣。至于版籍所载先系则又不可以为例何也。己有两子。甲承所后。乙承本生。甲以己为父而以所后为祖。乙以己为父而以本生为祖。是父则同而祖则异。其不可也明矣。题主与载籍。虽曰斑驳。外此别无以处也。若究言之。此事终是不成道理。所以有推不去处。只合遵 朝家所命之内。而其不得已者。亦无柰何。然孝之一字。妄谓书亦无妨。礼所云不称孝者。彼乃指支子而自别于宗者也。孝本是承祀为宗之名。孝孙者犹言承祀之孙也。不承则已。今既承而主祀矣。称孝而表其主祀。未见大妨。上书属称。下书旁注。非庶孙之事。既更无嫡孙在而身当宗嫡之地。题主而奉祀矣。何独于一孝字为嫌。纵使不称。亦恐无所益也。无后班祔之主。窃谓其属称与旁注。皆不须书。粉面之制。本为宗法而设。下而支子之不敢抗。上而旁亲之不宜题也。只书生时称号而易世不改者也。府君之称。施于所尊。若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不当云尔。若其亡于父兄在时而不复改题。则不但殇丧为然。无后之主亦无府君之称矣。且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5H 页
 据语类云无爵曰府君夫人。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谓之明府。今人亦谓父为家府也。故家礼祝版条无爵称府君夫人。而皆成人之号也。女而殇死不可称夫人。则府君之题。恐亦未安。未知如何。
据语类云无爵曰府君夫人。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谓之明府。今人亦谓父为家府也。故家礼祝版条无爵称府君夫人。而皆成人之号也。女而殇死不可称夫人。则府君之题。恐亦未安。未知如何。答李仲皓(汉辅)别纸(丁未)
别子为祖而嫡嗣无人则到今择以立宗无可疑者。况 朝廷处分之已定耶。今见定宗孙。其祖若祢。虽非当时承宗之嫡。宗既有归。其未承犹承也。宗孙不可以追继既绝之长泒。又不宗其祖祢则彼宗果何从而传统来也。汉人建议以孔氏为殷之世。程子引以證立宗之礼。而有旁枝达干之说则夺宗之义。亦可以通于士庶矣。通典数条亦然。大儿无子。小儿有子。小儿之子应服三年。彼小儿之子若入系为大儿之子。则此何容议为。此分明非入系者。而承祖之重。他日岂可以其父之始非嫡嗣之故。而不入于庙乎。所谕兄亡弟及。亦古道然也。礼云嫡妇不为舅后者。姑为之小功。此谓子虽嫡长。或无子而死。不得传重则其妻不得为嫡妇。故服之以庶妇也。然则宗之所归。必于支子。而支子虽已先亡。其子又可传重。通典所论。亦似有据。古者世各异庙。惟官师位卑。故祖祢共庙。则异庙之重于同庙者可知。自东京以来。同堂异室之制。自天子达。未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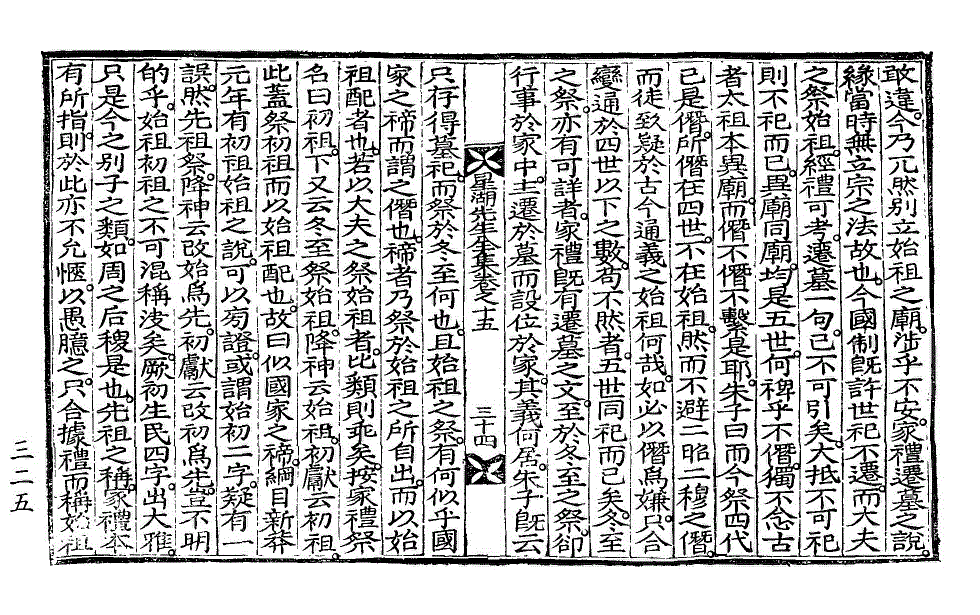 敢违。今乃兀然别立始祖之庙。涉乎不安。家礼迁墓之说。缘当时无立宗之法故也。今国制既许世祀不迁。而大夫之祭始祖。经礼可考。迁墓一句。已不可引矣。大抵不可祀则不祀而已。异庙同庙。均是五世。何裨乎不僭。独不念古者太祖本异庙。而僭不僭不系是耶。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是僭。所僭在四世。不在始祖。然而不避二昭二穆之僭。而徒致疑于古今通义之始祖何哉。如必以僭为嫌。只合变通于四世以下之数。苟不然者。五世同祀而已矣。冬至之祭。亦有可详者。家礼既有迁墓之文。至于冬至之祭。却行事于家中。主迁于墓而设位于家。其义何居。朱子既云只存得墓祀。而祭于冬至何也。且始祖之祭。有何似乎国家之禘而谓之僭也。禘者乃祭于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者也。若以大夫之祭始祖者。比类则乖矣。按家礼祭名曰初祖。下又云冬至祭始祖。降神云始祖。初献云初祖。此盖祭初祖而以始祖配也。故曰似国家之禘。纲目新莽元年有初祖始祖之说。可以旁證。或谓始初二字。疑有一误。然先祖祭。降神云改始为先。初献云改初为先。岂不明的乎。始祖初祖之不可混称决矣。厥初生民四字。出大雅。只是今之别子之类。如周之后稷是也。先祖之称。家礼本有所指。则于此亦不允惬。以愚臆之。只合据礼而称始祖
敢违。今乃兀然别立始祖之庙。涉乎不安。家礼迁墓之说。缘当时无立宗之法故也。今国制既许世祀不迁。而大夫之祭始祖。经礼可考。迁墓一句。已不可引矣。大抵不可祀则不祀而已。异庙同庙。均是五世。何裨乎不僭。独不念古者太祖本异庙。而僭不僭不系是耶。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是僭。所僭在四世。不在始祖。然而不避二昭二穆之僭。而徒致疑于古今通义之始祖何哉。如必以僭为嫌。只合变通于四世以下之数。苟不然者。五世同祀而已矣。冬至之祭。亦有可详者。家礼既有迁墓之文。至于冬至之祭。却行事于家中。主迁于墓而设位于家。其义何居。朱子既云只存得墓祀。而祭于冬至何也。且始祖之祭。有何似乎国家之禘而谓之僭也。禘者乃祭于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者也。若以大夫之祭始祖者。比类则乖矣。按家礼祭名曰初祖。下又云冬至祭始祖。降神云始祖。初献云初祖。此盖祭初祖而以始祖配也。故曰似国家之禘。纲目新莽元年有初祖始祖之说。可以旁證。或谓始初二字。疑有一误。然先祖祭。降神云改始为先。初献云改初为先。岂不明的乎。始祖初祖之不可混称决矣。厥初生民四字。出大雅。只是今之别子之类。如周之后稷是也。先祖之称。家礼本有所指。则于此亦不允惬。以愚臆之。只合据礼而称始祖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6H 页
 也。旁题则家礼祝辞虽云孝孙。而与祖考主面无别。依程礼称孝远孙又似无妨。而彼或是于初祖故云尔。是未可知。然则称孝几世孙可耶。盖始祖之称。百世无变。而后孙之称。世各不同。其势恐然。而依孝宁家属称。旁题并称几世又何妨。然既为始祖。祝告当称始祖。用此题主。尤觉妥安。立宗而主祀矣。又何可阙孝字耶。具书姓名之说。彼必因初祖祭初献祝辞而云。然彼初祖者或是受姓以前故耳。据降神祝辞则可见。冬至之僭。既经断案。忌祭是一日之丧。而后世之所义起。世数既远。亦恐当废。所可举者时享也。时享则与群主合祀。而若或以不能遍行乎群主为虑。则依家礼岁一祭之例。择日奉主行事如何。墓祭亦依岁一祭之例。或择日于三月上旬。或用寒食。无所不可。俗节朔日之荐。似不可不举矣。左旁之说。不须多话。主式方出于伊川。而其图题于人之左。今之所遵者家礼之文。而朱子跋人书卷。谓书于左旁者极多。如跋范文正家书则又并录本书于右。其为人左者无疑。均是朱子之笔。岂容异例。如何氏小学图者。何据而云然。用腥一端。尝考古礼即僭也。家礼初祖祭。惟首心肝肺用腥。其馀皆熟。又未闻用生鱼者也。家礼时祭条有鱼肉字。不著生熟。人遂执以为用腥。殊不知家礼更无荐熟之文。此盖通指庶羞之类。
也。旁题则家礼祝辞虽云孝孙。而与祖考主面无别。依程礼称孝远孙又似无妨。而彼或是于初祖故云尔。是未可知。然则称孝几世孙可耶。盖始祖之称。百世无变。而后孙之称。世各不同。其势恐然。而依孝宁家属称。旁题并称几世又何妨。然既为始祖。祝告当称始祖。用此题主。尤觉妥安。立宗而主祀矣。又何可阙孝字耶。具书姓名之说。彼必因初祖祭初献祝辞而云。然彼初祖者或是受姓以前故耳。据降神祝辞则可见。冬至之僭。既经断案。忌祭是一日之丧。而后世之所义起。世数既远。亦恐当废。所可举者时享也。时享则与群主合祀。而若或以不能遍行乎群主为虑。则依家礼岁一祭之例。择日奉主行事如何。墓祭亦依岁一祭之例。或择日于三月上旬。或用寒食。无所不可。俗节朔日之荐。似不可不举矣。左旁之说。不须多话。主式方出于伊川。而其图题于人之左。今之所遵者家礼之文。而朱子跋人书卷。谓书于左旁者极多。如跋范文正家书则又并录本书于右。其为人左者无疑。均是朱子之笔。岂容异例。如何氏小学图者。何据而云然。用腥一端。尝考古礼即僭也。家礼初祖祭。惟首心肝肺用腥。其馀皆熟。又未闻用生鱼者也。家礼时祭条有鱼肉字。不著生熟。人遂执以为用腥。殊不知家礼更无荐熟之文。此盖通指庶羞之类。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第 3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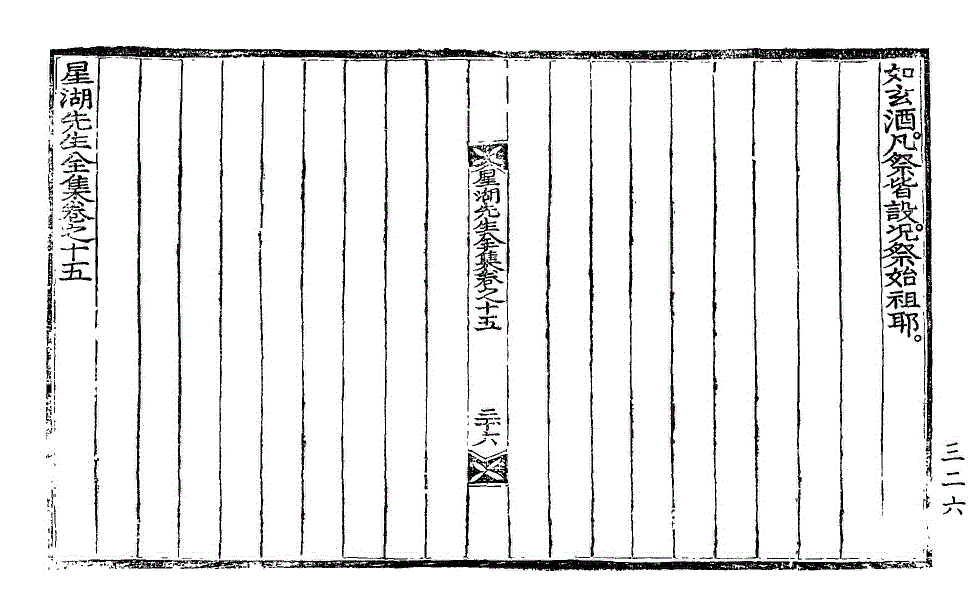 如玄酒。凡祭皆设。况祭始祖耶。
如玄酒。凡祭皆设。况祭始祖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