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x 页
药山漫稿卷之九
书筵讲义
书筵讲义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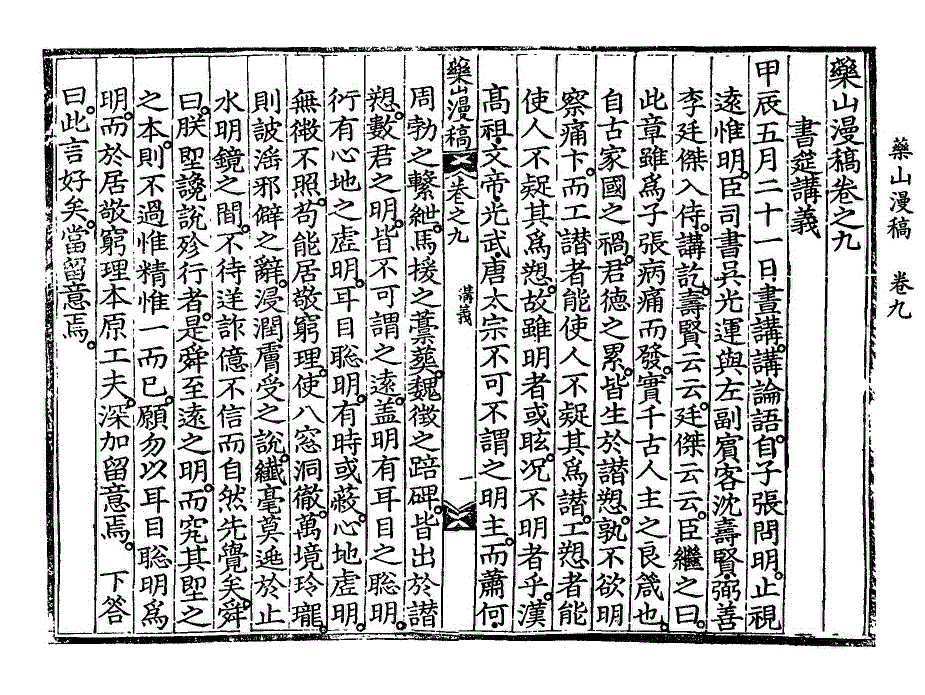 [书筵讲义]
[书筵讲义]甲辰
五月
二十一日昼讲。讲论语。自子张问明。止视远惟明。臣司书吴光运与左副宾客沈寿贤,弼善李廷杰入侍。讲讫。寿贤云云。廷杰云云。臣继之曰。此章虽为子张病痛而发。实千古人主之良箴也。自古家国之祸。君德之累。皆生于谮愬。孰不欲明察痛卞。而工谮者能使人不疑其为谮。工愬者能使人不疑其为愬。故虽明者或眩。况不明者乎。汉高祖,文帝,光武,唐太宗不可不谓之明主。而萧何,周勃之系绁。马援之藁葬。魏徵之踣碑。皆出于谮愬。数君之明。皆不可谓之远。盖明有耳目之聪明。衍有心地之虚明。耳目聪明。有时或蔽。心地虚明。无微不照。苟能居敬穷理。使八窗洞彻。万境玲珑。则诐淫邪僻之辞。浸润肤受之说。纤毫莫逃于止水明镜之间。不待逆诈亿不信而自然先觉矣。舜曰。朕堲谗说殄行者。是舜至远之明。而究其堲之之本。则不过惟精惟一而已。愿勿以耳目聪明为明。而于居敬穷理本原工夫。深加留意焉。 下答曰。此言好矣。当留意焉。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0L 页
 是日召对。臣及弼善李廷杰入侍。讲讫。臣论宋主杀义康曰。兄弟骨肉也。莫如我兄弟。难得者兄弟。于是而一有所未尽。则贼天之彝。斁人之伦。夫叔段之稔恶。可谓难化之人。而郑庄受郑考之名。厉王之不轨。可谓难赦之罪。而汉文贻斗粟之讥。况义康之过失。亦不至如叔段,厉王者乎。宋文帝授以权而使之骄恣。逆未著而置之诛戮。友爱之天牿矣。宋文可谓千古罪人矣。故大书于纲。笔法严矣。下答曰。然矣。义康虽有过失。而反逆未著。遽加诛戮。天理灭矣。臣又论魏主遗臧质书。卿若杀之。无所不利曰。佛狸之败。决于此一言矣。丁零胡氐羌。皆其与国。又与之连师伐宋。则诗所谓与子同仇者。而乃反以杀之无所不利为言。其心之阴贼不忍。有如此者。以此贼心待之。则诸国亦岂尽心同事乎。佛狸之败。在于杀之一字矣。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魏人杀掠丁壮。斩截婴儿贯槊曰。当时人以卯年之谣。验佛狸之死。而臣则以为童谣荒诞。虽或偶合。乌可信也。但天道神明。杀人如此而未有令终其身者。臣以斩截贯槊等事。为佛狸不得其死之验耳。 下答曰。然矣。贯槊盘舞之说。残忍
是日召对。臣及弼善李廷杰入侍。讲讫。臣论宋主杀义康曰。兄弟骨肉也。莫如我兄弟。难得者兄弟。于是而一有所未尽。则贼天之彝。斁人之伦。夫叔段之稔恶。可谓难化之人。而郑庄受郑考之名。厉王之不轨。可谓难赦之罪。而汉文贻斗粟之讥。况义康之过失。亦不至如叔段,厉王者乎。宋文帝授以权而使之骄恣。逆未著而置之诛戮。友爱之天牿矣。宋文可谓千古罪人矣。故大书于纲。笔法严矣。下答曰。然矣。义康虽有过失。而反逆未著。遽加诛戮。天理灭矣。臣又论魏主遗臧质书。卿若杀之。无所不利曰。佛狸之败。决于此一言矣。丁零胡氐羌。皆其与国。又与之连师伐宋。则诗所谓与子同仇者。而乃反以杀之无所不利为言。其心之阴贼不忍。有如此者。以此贼心待之。则诸国亦岂尽心同事乎。佛狸之败。在于杀之一字矣。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魏人杀掠丁壮。斩截婴儿贯槊曰。当时人以卯年之谣。验佛狸之死。而臣则以为童谣荒诞。虽或偶合。乌可信也。但天道神明。杀人如此而未有令终其身者。臣以斩截贯槊等事。为佛狸不得其死之验耳。 下答曰。然矣。贯槊盘舞之说。残忍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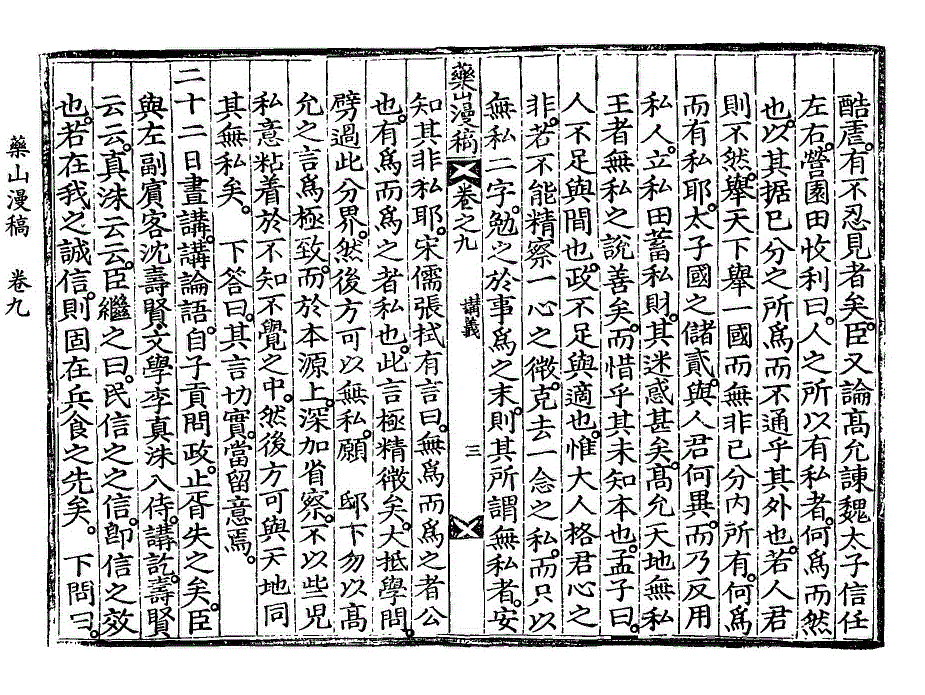 酷虐。有不忍见者矣。臣又论高允谏魏太子信任左右。营园田收利曰。人之所以有私者。何为而然也。以其据己分之所为而不通乎其外也。若人君则不然。举天下举一国而无非己分内所有。何为而有私耶。太子国之储贰。与人君何异。而乃反用私人。立私田蓄私财。其迷惑甚矣。高允天地无私王者无私之说善矣。而惜乎其未知本也。孟子曰。人不足与间也。政不足与适也。惟大人格君心之非。若不能精察一心之微。克去一念之私。而只以无私二字。勉之于事为之末。则其所谓无私者。安知其非私耶。宋儒张拭有言曰。无为而为之者公也。有为而为之者私也。此言极精微矣。大抵学问。劈过此分界。然后方可以无私。愿 邸下勿以高允之言为极致。而于本源上。深加省察。不以些儿私意粘着于不知不觉之中。然后方可与天地同其无私矣。 下答曰。其言切实。当留意焉。
酷虐。有不忍见者矣。臣又论高允谏魏太子信任左右。营园田收利曰。人之所以有私者。何为而然也。以其据己分之所为而不通乎其外也。若人君则不然。举天下举一国而无非己分内所有。何为而有私耶。太子国之储贰。与人君何异。而乃反用私人。立私田蓄私财。其迷惑甚矣。高允天地无私王者无私之说善矣。而惜乎其未知本也。孟子曰。人不足与间也。政不足与适也。惟大人格君心之非。若不能精察一心之微。克去一念之私。而只以无私二字。勉之于事为之末。则其所谓无私者。安知其非私耶。宋儒张拭有言曰。无为而为之者公也。有为而为之者私也。此言极精微矣。大抵学问。劈过此分界。然后方可以无私。愿 邸下勿以高允之言为极致。而于本源上。深加省察。不以些儿私意粘着于不知不觉之中。然后方可与天地同其无私矣。 下答曰。其言切实。当留意焉。二十二日昼讲。讲论语。自子贡问政。止胥失之矣。臣与左副宾客沈寿贤,文学李真洙入侍。讲讫。寿贤云云。真洙云云。臣继之曰。民信之之信。即信之效也。若在我之诚信。则固在兵食之先矣。 下问曰。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1L 页
 然则孔子之教。何不先及在我之诚信。臣曰。若他人问之。则孔子必以教化诚信字。加之于兵食之上矣。至如子贡。则于诚信教化之道。固已讲之熟矣。明知为国之本。不外于此。而今此问政。不过设施之方。则孔子亦以设施次第告之。非谓足食足兵然后始敷我之诚信也。诚信行于兵食之间。而兵食在于诚信之中。固未尝今日足兵食而明日施诚信也。又未尝今日施诚信而明日足兵食也。凡言次第之类。多如此。如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者。亦非谓今日格物而明日致知。又明日正心也。初学者若曰吾不能格物。姑不可以正心修身云尔。则岂非谬戾之甚者乎。凡言次第先后之类。多如此矣。 下答曰。剖析明矣。其引学问次第之说。尤好矣。臣又论棘子成子贡之说曰。文质等耳两说。皆过矣。然以孔子大林放,吾从先进与奢宁俭之教观之。则文质轻重之分可见。而且周末弥文。几乎灭质。故圣人之教。必以本为崇。盖亦随时通变之意也。臣伏念我 朝亦为尚文之治。即今繁文琐节。不特周末之弊而已。孔子则下而为臣。故不能救当时之弊。
然则孔子之教。何不先及在我之诚信。臣曰。若他人问之。则孔子必以教化诚信字。加之于兵食之上矣。至如子贡。则于诚信教化之道。固已讲之熟矣。明知为国之本。不外于此。而今此问政。不过设施之方。则孔子亦以设施次第告之。非谓足食足兵然后始敷我之诚信也。诚信行于兵食之间。而兵食在于诚信之中。固未尝今日足兵食而明日施诚信也。又未尝今日施诚信而明日足兵食也。凡言次第之类。多如此。如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者。亦非谓今日格物而明日致知。又明日正心也。初学者若曰吾不能格物。姑不可以正心修身云尔。则岂非谬戾之甚者乎。凡言次第先后之类。多如此矣。 下答曰。剖析明矣。其引学问次第之说。尤好矣。臣又论棘子成子贡之说曰。文质等耳两说。皆过矣。然以孔子大林放,吾从先进与奢宁俭之教观之。则文质轻重之分可见。而且周末弥文。几乎灭质。故圣人之教。必以本为崇。盖亦随时通变之意也。臣伏念我 朝亦为尚文之治。即今繁文琐节。不特周末之弊而已。孔子则下而为臣。故不能救当时之弊。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2H 页
 若在上者则不可诿之于时弊。而不思矫弊之道也。须于此等处留意焉。 下答曰。其言切实矣。
若在上者则不可诿之于时弊。而不思矫弊之道也。须于此等处留意焉。 下答曰。其言切实矣。是日夕讲。讲纲目。自宋元嘉二十九年。止亲为沙门下发。臣与左副宾客沈寿贤,文学李真洙入侍。讲讫。寿贤曰。今日讲读处。皆弑逆大变。此等处不必讲。说文义阔略可矣。臣曰。不然。唐时讲官有为此议论者。宋儒胡安国讥之以腐儒。因曰。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陷首恶之名。盖世道衰乱。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而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而乱贼惧。纲目亦春秋之凡例也。故于此等处。大书特书。使百世照人耳目。而庶几乱贼者惧。今若阔略此等处而不讲焉。则是岂作春秋之意耶。 下答曰。此等处。言之污口。予意亦欲阔略矣。今闻司书之言。最有所见。且有先儒定论云。当与他处同为讲读矣。臣因论宋文帝使徐爰衔中旨。授诸将方略。临时宣示。臣曰。兵难遥度。呼吸之间。机会万千。岂可预授方略而可以动中机宜耶。兵不战而可见其败矣。且不但用兵如此。大凡任人之道。贵在勿贰。如非其人则不任可也。如其人而任之。则岂可从傍掣肘乎。自古贤君委任而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2L 页
 成功。庸主疑贰而偾事。实是千古之龟鉴也。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古弼之死曰。古弼曾有笔公之名。以直谏著。而及今不能死节于弑逆之变。又不能立功于讨逆之谋。依附于乱贼之间。则其死非冤矣。 下答曰。古弼虽有直臣之名。而末梢如此。其死宜矣。如高允之名臣。而不见树立于此时何也。臣曰。高允参于讨宗爱之谋。观于南史资治等书。则高允之有功。可知矣。高允则与古弼异矣。臣又论魏复建佛图曰。 邸下睿学既高。释道之乱真。固不待臣等之说而想必洞然矣。固不必缕缕。而以此时事言之。魏世祖之屠戮沙门酷矣。其禁佛则是矣。屠戮已无及矣。为子孙者。惟当遵守佛禁可也。今乃复建佛图。其违先旨崇异端。贻讥百代。当如何哉。故纲目特书以讥之矣。 下答曰。然矣。
成功。庸主疑贰而偾事。实是千古之龟鉴也。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古弼之死曰。古弼曾有笔公之名。以直谏著。而及今不能死节于弑逆之变。又不能立功于讨逆之谋。依附于乱贼之间。则其死非冤矣。 下答曰。古弼虽有直臣之名。而末梢如此。其死宜矣。如高允之名臣。而不见树立于此时何也。臣曰。高允参于讨宗爱之谋。观于南史资治等书。则高允之有功。可知矣。高允则与古弼异矣。臣又论魏复建佛图曰。 邸下睿学既高。释道之乱真。固不待臣等之说而想必洞然矣。固不必缕缕。而以此时事言之。魏世祖之屠戮沙门酷矣。其禁佛则是矣。屠戮已无及矣。为子孙者。惟当遵守佛禁可也。今乃复建佛图。其违先旨崇异端。贻讥百代。当如何哉。故纲目特书以讥之矣。 下答曰。然矣。二十三日召对。讲纲目。自魏以周忸。止不忧不济。臣与文学李真洙入侍。讲讫。真洙云云。臣继之曰。此时胡乱甚矣。可谓长夜乾坤。今日所讲。尤无文义可论处。果如上番所达矣。然善善而感发。恶恶而惩创。其功一也。恶恶而至于无恶则纯善矣。善善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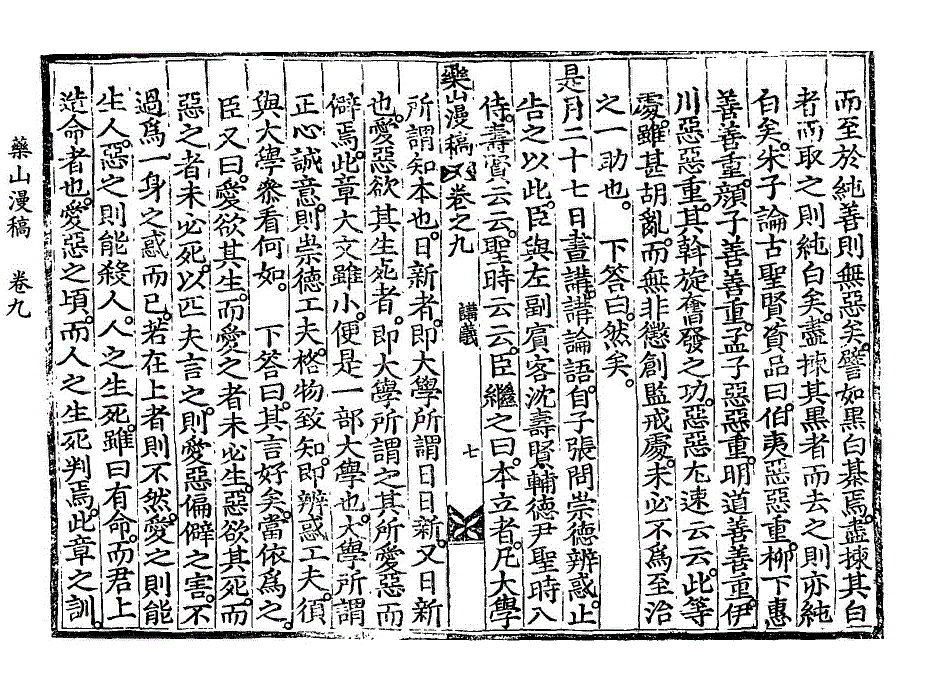 而至于纯善则无恶矣。譬如黑白棋焉。尽拣其白者而取之则纯白矣。尽拣其黑者而去之则亦纯白矣。朱子论古圣贤资品曰。伯夷恶恶重。柳下惠善善重。颜子善善重。孟子恶恶重。明道善善重。伊川恶恶重。其斡旋奋发之功。恶恶尤速云云。此等处。虽甚胡乱。而无非惩创监戒处。未必不为至治之一助也。 下答曰。然矣。
而至于纯善则无恶矣。譬如黑白棋焉。尽拣其白者而取之则纯白矣。尽拣其黑者而去之则亦纯白矣。朱子论古圣贤资品曰。伯夷恶恶重。柳下惠善善重。颜子善善重。孟子恶恶重。明道善善重。伊川恶恶重。其斡旋奋发之功。恶恶尤速云云。此等处。虽甚胡乱。而无非惩创监戒处。未必不为至治之一助也。 下答曰。然矣。是月二十七日昼讲。讲论语。自子张问崇德辨惑。止告之以此。臣与左副宾客沈寿贤,辅德尹圣时入侍。寿贤云云。圣时云云。臣继之曰。本立者。凡大学所谓知本也。日新者。即大学所谓日日新。又日新也。爱恶欲其生死者。即大学所谓之其所爱恶而僻焉。此章大文虽小。便是一部大学也。大学所谓正心诚意。则崇德工夫。格物致知。即辨惑工夫。须与大学参看何如。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依为之。臣又曰。爱欲其生。而爱之者未必生。恶欲其死。而恶之者未必死。以匹夫言之。则爱恶偏僻之害。不过为一身之惑而已。若在上者则不然。爱之则能生人。恶之则能杀人。人之生死。虽曰有命。而君上造命者也。爱恶之顷。而人之生死判焉。此章之训。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3L 页
 尤当为在上者之惕念处也。 下答曰。其言切实矣。
尤当为在上者之惕念处也。 下答曰。其言切实矣。是日召对。讲纲目。自宋大明四年。止不果施行。臣与辅德尹圣时入侍。讲讫。圣时云云。臣继之曰。宋孝武耕籍田立明堂。似乎复古礼矣。然礼乐待人而后行。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宋主杀谏臣残骨肉乱闺壸。而强行三代之礼。礼岂徒行乎。 下答曰。然则纲之大书。出于贬意乎。臣曰。非褒非贬。据实直书。而虚实得失自现。则不贬而自贬矣。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侍中谢庄不奉旨须墨敕乃开曰。庄可谓差强人意者。然庄亦未尽矣。庄与郅君章所处不同。郅君章居下位。唯当守门不奉诏而已。若庄者在于侍从之列。见君上逸豫荒淫之举。惟当扣头沥血。随事争执。不得其言则去。岂可须墨敕开门而已。 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庆之目不知书车马率素曰。庆之虽不学。而俭约避权如此。天资可谓美矣。然末年。与子业同辇。晚节无足观。亦出于不学。盖未有不学而能为完人者。虽以霍光之忠而不能正其妻之恶。况下此者乎。故人不可无学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顾法对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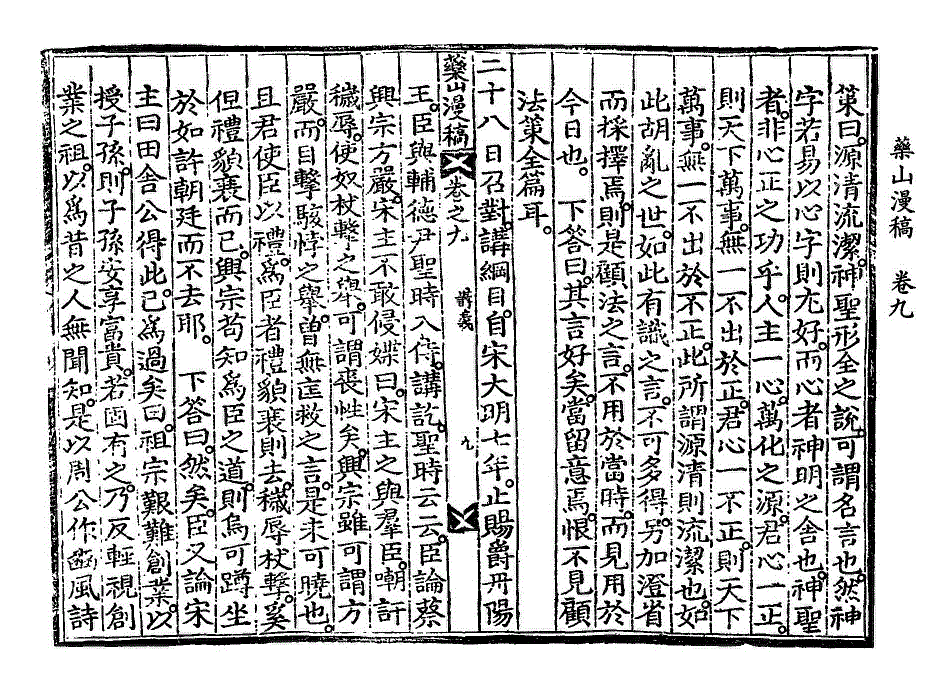 策曰。源清流洁。神圣形全之说。可谓名言也。然神字若易以心字则尤好。而心者神明之舍也。神圣者。非心正之功乎。人主一心。万化之源。君心一正。则天下万事。无一不出于正。君心一不正。则天下万事。无一不出于不正。此所谓源清则流洁也。如此胡乱之世。如此有识之言。不可多得。另加澄省而采择焉。则是顾法之言。不用于当时。而见用于今日也。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留意焉。恨不见顾法策全篇耳。
策曰。源清流洁。神圣形全之说。可谓名言也。然神字若易以心字则尤好。而心者神明之舍也。神圣者。非心正之功乎。人主一心。万化之源。君心一正。则天下万事。无一不出于正。君心一不正。则天下万事。无一不出于不正。此所谓源清则流洁也。如此胡乱之世。如此有识之言。不可多得。另加澄省而采择焉。则是顾法之言。不用于当时。而见用于今日也。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留意焉。恨不见顾法策全篇耳。二十八日召对。讲纲目。自宋大明七年。止赐爵丹阳王。臣与辅德尹圣时入侍。讲讫。圣时云云。臣论蔡兴宗方严。宋主不敢侵媟曰。宋主之与群臣。嘲讦秽辱。使奴杖击之举。可谓丧性矣。兴宗虽可谓方严。而目击骇悖之举。曾无匡救之言。是未可晓也。且君使臣以礼。为臣者礼貌衰则去。秽辱杖击。奚但礼貌衰而已。兴宗苟知为臣之道。则乌可蹲坐于如许朝廷而不去耶。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曰。祖宗艰难创业。以授子孙。则子孙安享富贵。若固有之。乃反轻视创业之祖。以为昔之人无闻知。是以周公作豳风诗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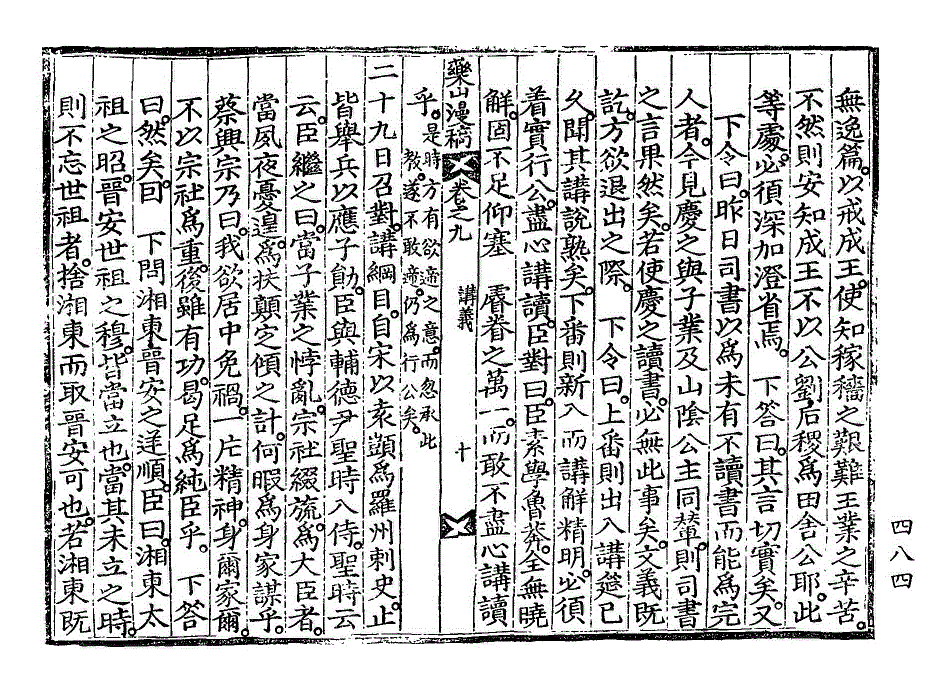 无逸篇。以戒成王。使知稼穑之艰难王业之辛苦。不然则安知成王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公耶。此等处。必须深加澄省焉。 下答曰。其言切实矣。又 下令曰。昨日司书以为未有不读书而能为完人者。今见庆之与子业及山阴公主同辇。则司书之言果然矣。若使庆之读书。必无此事矣。文义既讫。方欲退出之际。 下令曰。上番则出入讲筵已久。闻其讲说熟矣。下番则新入而讲解精明。必须着实行公。尽心讲读。臣对曰。臣素学鲁莽。全无晓解。固不足仰塞 睿眷之万一。而敢不尽心讲读乎。(是时方有欲遆之意。而忽承此 教。遂不敢遆。仍为行公矣。)
无逸篇。以戒成王。使知稼穑之艰难王业之辛苦。不然则安知成王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公耶。此等处。必须深加澄省焉。 下答曰。其言切实矣。又 下令曰。昨日司书以为未有不读书而能为完人者。今见庆之与子业及山阴公主同辇。则司书之言果然矣。若使庆之读书。必无此事矣。文义既讫。方欲退出之际。 下令曰。上番则出入讲筵已久。闻其讲说熟矣。下番则新入而讲解精明。必须着实行公。尽心讲读。臣对曰。臣素学鲁莽。全无晓解。固不足仰塞 睿眷之万一。而敢不尽心讲读乎。(是时方有欲遆之意。而忽承此 教。遂不敢遆。仍为行公矣。)二十九日召对。讲纲目。自宋以袁顗为罗州刺史。止皆举兵以应子勋。臣与辅德尹圣时入侍。圣时云云。臣继之曰。当子业之悖乱。宗社缀旒。为大臣者。当夙夜忧遑。为扶颠定倾之计。何暇为身家谋乎。蔡兴宗乃曰。我欲居中免祸。一片精神。身尔家尔。不以宗社为重。后虽有功。曷足为纯臣乎。 下答曰。然矣。因 下问湘东,晋安之逆顺。臣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皆当立也。当其未立之时。则不忘世祖者。舍湘东而取晋安可也。若湘东既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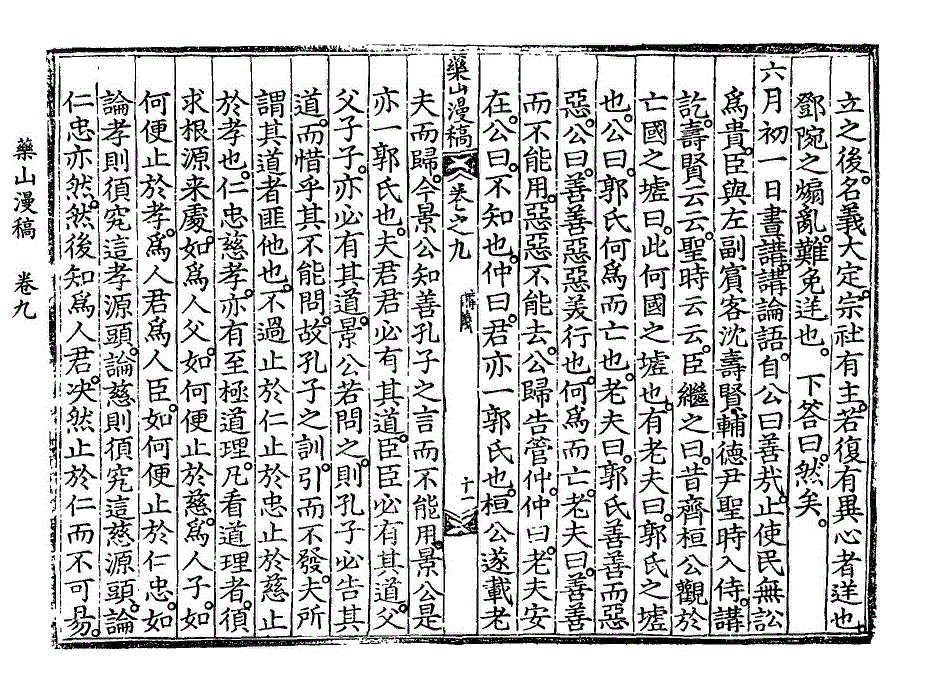 立之后。名义大定。宗社有主。若复有异心者逆也。邓𨺋之煽乱。难免逆也。 下答曰。然矣。
立之后。名义大定。宗社有主。若复有异心者逆也。邓𨺋之煽乱。难免逆也。 下答曰。然矣。六月
初一日昼讲。讲论语。自公曰善哉。止使民无讼为贵。臣与左副宾客沈寿贤,辅德尹圣时入侍。讲讫。寿贤云云。圣时云云。臣继之曰。昔齐桓公观于亡国之墟曰。此何国之墟也。有老夫曰。郭氏之墟也。公曰。郭氏何为而亡也。老夫曰。郭氏善善而恶恶。公曰。善善恶恶美行也。何为而亡。老夫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公归告管仲。仲曰。老夫安在。公曰。不知也。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桓公遂载老夫而归。今景公知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景公是亦一郭氏也。夫君君必有其道。臣臣必有其道。父父子子。亦必有其道。景公若问之。则孔子必告其道。而惜乎其不能问。故孔子之训。引而不发。夫所谓其道者匪他也。不过止于仁止于忠止于慈止于孝也。仁忠慈孝。亦有至极道理。凡看道理者。须求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忠。如论孝则须究这孝源头。论慈则须究这慈源头。论仁忠亦然。然后知为人君。决然止于仁而不可易。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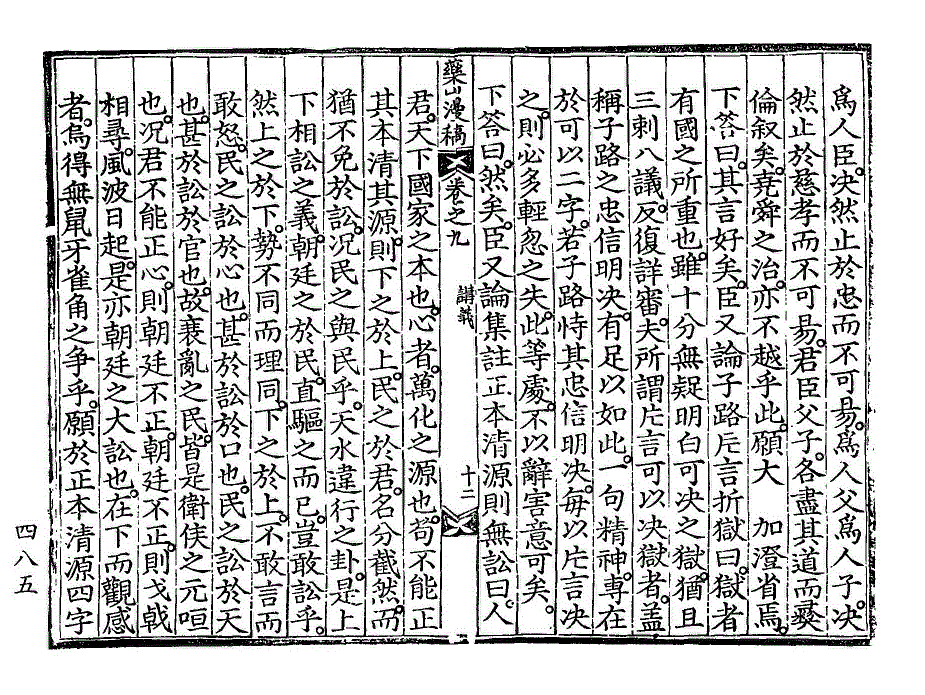 为人臣。决然止于忠而不可易。为人父为人子。决然止于慈孝而不可易。君臣父子。各尽其道而彝伦叙矣。尧舜之治。亦不越乎此。愿大 加澄省焉。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子路片言折狱曰。狱者有国之所重也。虽十分无疑明白可决之狱。犹且三刺八议。反复详审。夫所谓片言可以决狱者。盖称子路之忠信明决。有足以如此。一句精神。专在于可以二字。若子路恃其忠信明决。每以片言决之。则必多轻忽之失。此等处。不以辞害意可矣。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集注正本清源则无讼曰。人君。天下国家之本也。心者。万化之源也。苟不能正其本清其源。则下之于上。民之于君。名分截然。而犹不免于讼。况民之与民乎。天水违行之卦。是上下相讼之义。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岂敢讼乎。然上之于下。势不同而理同。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讼于心也。甚于讼于口也。民之讼于天也。甚于讼于官也。故衰乱之民。皆是卫侯之元咺也。况君不能正心。则朝廷不正。朝廷不正。则戈戟相寻。风波日起。是亦朝廷之大讼也。在下而观感者。乌得无鼠牙雀角之争乎。愿于正本清源四字
为人臣。决然止于忠而不可易。为人父为人子。决然止于慈孝而不可易。君臣父子。各尽其道而彝伦叙矣。尧舜之治。亦不越乎此。愿大 加澄省焉。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子路片言折狱曰。狱者有国之所重也。虽十分无疑明白可决之狱。犹且三刺八议。反复详审。夫所谓片言可以决狱者。盖称子路之忠信明决。有足以如此。一句精神。专在于可以二字。若子路恃其忠信明决。每以片言决之。则必多轻忽之失。此等处。不以辞害意可矣。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集注正本清源则无讼曰。人君。天下国家之本也。心者。万化之源也。苟不能正其本清其源。则下之于上。民之于君。名分截然。而犹不免于讼。况民之与民乎。天水违行之卦。是上下相讼之义。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岂敢讼乎。然上之于下。势不同而理同。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讼于心也。甚于讼于口也。民之讼于天也。甚于讼于官也。故衰乱之民。皆是卫侯之元咺也。况君不能正心。则朝廷不正。朝廷不正。则戈戟相寻。风波日起。是亦朝廷之大讼也。在下而观感者。乌得无鼠牙雀角之争乎。愿于正本清源四字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6H 页
 上。 深加省察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 下问曰。子路片言折狱。故朱子许之以忠信。而杨氏以为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以忠信之人。而不知以礼逊为国者何也。宾客宫僚。各陈所见为可。寿贤云云。真洙云云。臣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故子曰。绘事后素。素者忠信也。绘事者礼也。有忠信之美质。而未及学礼者有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十室之内。忠信之人则可得。而知礼之人则难得。子路以忠信之质。游于圣人之门。亦何尝不学礼。而资质粗疏。礼学未造精密处。所谓升堂未入室也。忠信与礼。等级次第分明。朱子杨氏之注。又何尝矛楯乎。 下答曰。闻司书之言。始晓然无疑矣。
上。 深加省察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 下问曰。子路片言折狱。故朱子许之以忠信。而杨氏以为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以忠信之人。而不知以礼逊为国者何也。宾客宫僚。各陈所见为可。寿贤云云。真洙云云。臣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故子曰。绘事后素。素者忠信也。绘事者礼也。有忠信之美质。而未及学礼者有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十室之内。忠信之人则可得。而知礼之人则难得。子路以忠信之质。游于圣人之门。亦何尝不学礼。而资质粗疏。礼学未造精密处。所谓升堂未入室也。忠信与礼。等级次第分明。朱子杨氏之注。又何尝矛楯乎。 下答曰。闻司书之言。始晓然无疑矣。初九日召对。讲纲目。自春正月。止珍奇奔寿阳。臣与文学赵尚庆入侍。讲讫。尚庆云云。臣论宋三叛事曰。人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方晋安之起兵也。宋明不自意有今日。而甫致平定。荒淫穷黩。比诸前日之开诚布款。判若二人。遂致长淮陷而三叛起。矜之一字。实危乱之先驱也。以尧舜禹汤之圣。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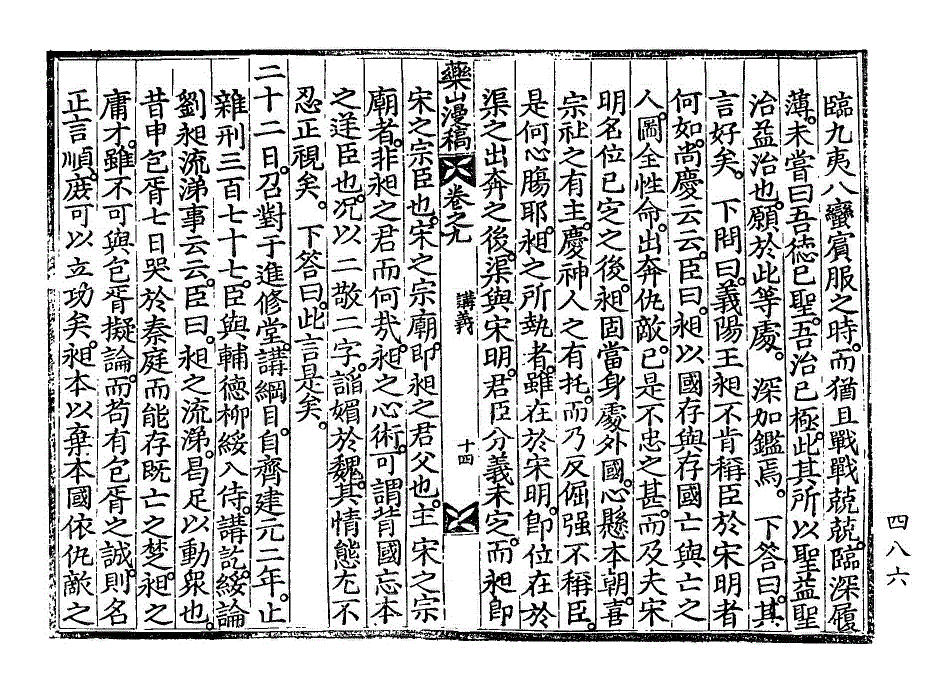 临九夷八蛮宾服之时。而犹且战战兢兢。临深履薄。未尝曰吾德已圣。吾治已极。此其所以圣益圣治益治也。愿于此等处。 深加鉴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 下问曰。义阳王昶不肯称臣于宋明者何如。尚庆云云。臣曰。昶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人。图全性命。出奔仇敌。已是不忠之甚。而及夫宋明名位已定之后。昶固当身处外国。心悬本朝。喜宗社之有主。庆神人之有托。而乃反倔强不称臣。是何心肠耶。昶之所执者。虽在于宋明。即位在于渠之出奔之后。渠与宋明。君臣分义未定。而昶即宋之宗臣也。宋之宗庙。即昶之君父也。主宋之宗庙者。非昶之君而何哉。昶之心术。可谓背国忘本之逆臣也。况以二敬二字。谄媚于魏。其情态尤不忍正视矣。 下答曰。此言是矣。
临九夷八蛮宾服之时。而犹且战战兢兢。临深履薄。未尝曰吾德已圣。吾治已极。此其所以圣益圣治益治也。愿于此等处。 深加鉴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 下问曰。义阳王昶不肯称臣于宋明者何如。尚庆云云。臣曰。昶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人。图全性命。出奔仇敌。已是不忠之甚。而及夫宋明名位已定之后。昶固当身处外国。心悬本朝。喜宗社之有主。庆神人之有托。而乃反倔强不称臣。是何心肠耶。昶之所执者。虽在于宋明。即位在于渠之出奔之后。渠与宋明。君臣分义未定。而昶即宋之宗臣也。宋之宗庙。即昶之君父也。主宋之宗庙者。非昶之君而何哉。昶之心术。可谓背国忘本之逆臣也。况以二敬二字。谄媚于魏。其情态尤不忍正视矣。 下答曰。此言是矣。二十二日。召对于进修堂。讲纲目。自齐建元二年。止杂刑三百七十七。臣与辅德柳绥入侍。讲讫。绥论刘昶流涕事云云。臣曰。昶之流涕。曷足以动众也。昔申包胥七日哭于秦庭而能存既亡之楚。昶之庸才。虽不可与包胥拟论。而苟有包胥之诚。则名正言顺。庶可以立功矣。昶本以弃本国依仇敌之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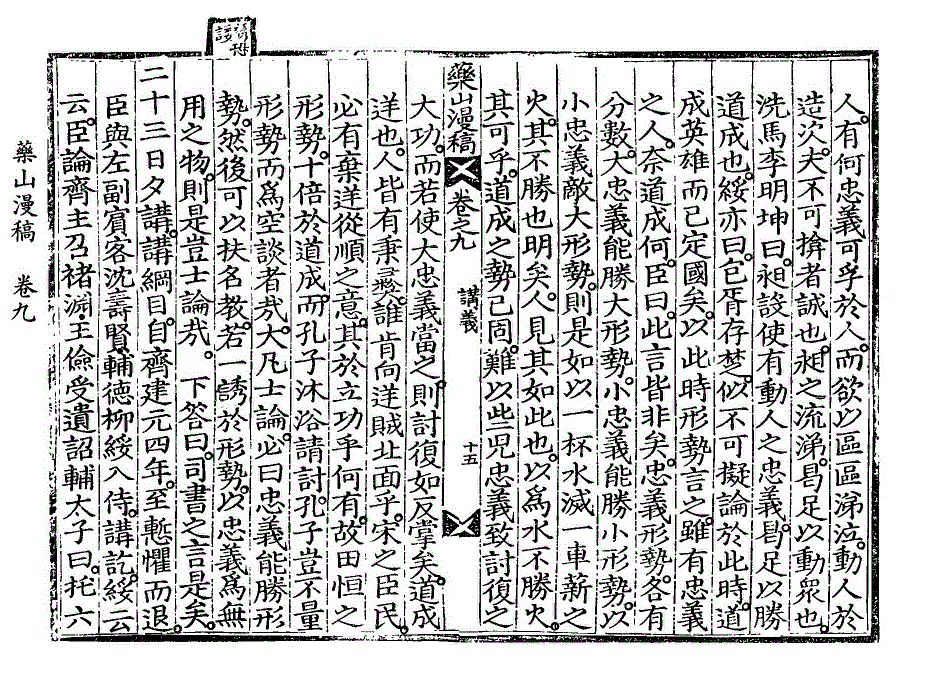 人。有何忠义可孚于人。而欲以区区涕泣。动人于造次。夫不可掩者诚也。昶之流涕。曷足以动众也。洗马李明坤曰。昶设使有动人之忠义。曷足以胜道成也。绥亦曰。包胥存楚。似不可拟论于此时。道成英雄而已定国矣。以此时形势言之。虽有忠义之人。奈道成何。臣曰。此言皆非矣。忠义形势。各有分数。大忠义能胜大形势。小忠义能胜小形势。以小忠义敌大形势。则是如以一杯水灭一车薪之火。其不胜也明矣。人见其如此也。以为水不胜火。其可乎。道成之势已固。难以些儿忠义致讨复之大功。而若使大忠义当之。则讨复如反掌矣。道成逆也。人皆有秉彝。谁肯向逆贼北面乎。宋之臣民。必有弃逆从顺之意。其于立功乎何有。故田恒之形势。十倍于道成。而孔子沐浴请讨。孔子岂不量形势而为空谈者哉。大凡士论。必曰忠义能胜形势。然后可以扶名教。若一诱(诱恐诿)于形势。以忠义为无用之物。则是岂士论哉。 下答曰。司书之言是矣。
人。有何忠义可孚于人。而欲以区区涕泣。动人于造次。夫不可掩者诚也。昶之流涕。曷足以动众也。洗马李明坤曰。昶设使有动人之忠义。曷足以胜道成也。绥亦曰。包胥存楚。似不可拟论于此时。道成英雄而已定国矣。以此时形势言之。虽有忠义之人。奈道成何。臣曰。此言皆非矣。忠义形势。各有分数。大忠义能胜大形势。小忠义能胜小形势。以小忠义敌大形势。则是如以一杯水灭一车薪之火。其不胜也明矣。人见其如此也。以为水不胜火。其可乎。道成之势已固。难以些儿忠义致讨复之大功。而若使大忠义当之。则讨复如反掌矣。道成逆也。人皆有秉彝。谁肯向逆贼北面乎。宋之臣民。必有弃逆从顺之意。其于立功乎何有。故田恒之形势。十倍于道成。而孔子沐浴请讨。孔子岂不量形势而为空谈者哉。大凡士论。必曰忠义能胜形势。然后可以扶名教。若一诱(诱恐诿)于形势。以忠义为无用之物。则是岂士论哉。 下答曰。司书之言是矣。二十三日夕讲。讲纲目。自齐建元四年。至惭惧而退。臣与左副宾客沈寿贤,辅德柳绥入侍。讲讫。绥云云。臣论齐主召褚渊,王俭受遗诏辅太子曰。托六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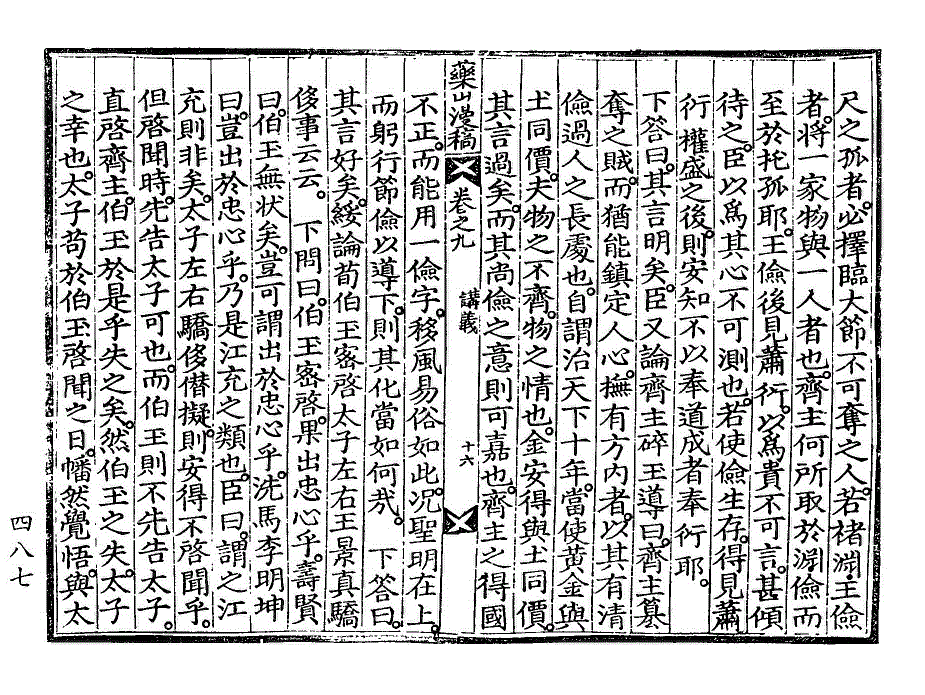 尺之孤者。必择临大节不可夺之人。若褚渊,王俭者。将一家物与一人者也。齐主何所取于渊,俭而至于托孤耶。王俭后见萧衍。以为贵不可言。甚倾待之。臣以为其心不可测也。若使俭生存。得见萧衍权盛之后。则安知不以奉道成者奉衍耶。 下答曰。其言明矣。臣又论齐主碎玉导曰。齐主篡夺之贼。而犹能镇定人心。抚有方内者。以其有清俭过人之长处也。自谓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金安得与土同价。其言过矣。而其尚俭之意则可嘉也。齐主之得国不正。而能用一俭字。移风易俗如此。况圣明在上。而躬行节俭以导下。则其化当如何哉。 下答曰。其言好矣。绥论荀伯玉密启太子左右王景真骄侈事云云。 下问曰。伯玉密启。果出忠心乎。寿贤曰。伯玉无状矣。岂可谓出于忠心乎。洗马李明坤曰。岂出于忠心乎。乃是江充之类也。臣曰。谓之江充则非矣。太子左右骄侈僭拟。则安得不启闻乎。但启闻时。先告太子可也。而伯玉则不先告太子。直启齐主。伯玉于是乎失之矣。然伯玉之失。太子之幸也。太子苟于伯玉启闻之日。幡然觉悟。与太
尺之孤者。必择临大节不可夺之人。若褚渊,王俭者。将一家物与一人者也。齐主何所取于渊,俭而至于托孤耶。王俭后见萧衍。以为贵不可言。甚倾待之。臣以为其心不可测也。若使俭生存。得见萧衍权盛之后。则安知不以奉道成者奉衍耶。 下答曰。其言明矣。臣又论齐主碎玉导曰。齐主篡夺之贼。而犹能镇定人心。抚有方内者。以其有清俭过人之长处也。自谓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金安得与土同价。其言过矣。而其尚俭之意则可嘉也。齐主之得国不正。而能用一俭字。移风易俗如此。况圣明在上。而躬行节俭以导下。则其化当如何哉。 下答曰。其言好矣。绥论荀伯玉密启太子左右王景真骄侈事云云。 下问曰。伯玉密启。果出忠心乎。寿贤曰。伯玉无状矣。岂可谓出于忠心乎。洗马李明坤曰。岂出于忠心乎。乃是江充之类也。臣曰。谓之江充则非矣。太子左右骄侈僭拟。则安得不启闻乎。但启闻时。先告太子可也。而伯玉则不先告太子。直启齐主。伯玉于是乎失之矣。然伯玉之失。太子之幸也。太子苟于伯玉启闻之日。幡然觉悟。与太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8H 页
 祖同其怒而诛景真之罪。与太祖同其亲信而宠伯玉之直。则岂不有光于太子乎。乃反以怒景真者怒伯玉。至于忧惧称疾则惑之甚矣。太祖亦当谆谆诲责。使之后勿如是而已。何至于弥月怒不解乎。可谓父子君臣交相失矣。而太子之失偏重。至于即祚之后。诬伯玉而杀之。其忘先王雠匹夫。遂非恶直。不孝不仁。莫甚于此矣。其何以为辅世长民之主乎。 下答曰。司书之言切当矣。臣又论齐武应天以实。不以文之说曰。以外面看之。似乎君人之言也。齐主果能应天以实。则茹法亮,吕文显之贪饕专恣。何为而不黜耶。齐主可谓应天以文而不以实也。欲以饰非之言。为听闻之美。人虽可欺。天可欺乎。此所以齐之天变叠出于此后。其亦异于宋景公三言退荧惑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
祖同其怒而诛景真之罪。与太祖同其亲信而宠伯玉之直。则岂不有光于太子乎。乃反以怒景真者怒伯玉。至于忧惧称疾则惑之甚矣。太祖亦当谆谆诲责。使之后勿如是而已。何至于弥月怒不解乎。可谓父子君臣交相失矣。而太子之失偏重。至于即祚之后。诬伯玉而杀之。其忘先王雠匹夫。遂非恶直。不孝不仁。莫甚于此矣。其何以为辅世长民之主乎。 下答曰。司书之言切当矣。臣又论齐武应天以实。不以文之说曰。以外面看之。似乎君人之言也。齐主果能应天以实。则茹法亮,吕文显之贪饕专恣。何为而不黜耶。齐主可谓应天以文而不以实也。欲以饰非之言。为听闻之美。人虽可欺。天可欺乎。此所以齐之天变叠出于此后。其亦异于宋景公三言退荧惑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二十四日昼讲。讲论语。自子曰其身正。止其能然乎。臣与左宾客赵泰亿。兼辅德赵锡命入侍。讲讫。泰亿云云。锡命云云。臣论其身正。不令而行。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时命令。见于典记者。何尝申申烦复乎。叔季以后。令如牛毛。修饰文词。观其言。虽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8L 页
 三代之教。何以加焉。然民之从之者。什不一二焉。言语末也。以言语感人。其效浅矣。况以命令驱人。人谁从之。欲行其令者。须以正身为主。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故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治国平天下。皆本于此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公子荆居室注曰。聊且属循序。粗略属有节。不欲速属循序。不尽美属有节。苟字则含包两意。而以最初一苟字观之。则见其不尽美之意。合三苟字而观之。则见其不欲速之意矣。 下答曰。然矣。臣又曰。骄吝奢侈之戒。宾客所达。缕缕详悉。臣不赘陈。而第苟字用处各别。用之于居室什物之间。则苟是好个字。用之于身心学问之际。则为不好个字。学问者若以聊且粗略为安。而曰斯亦足矣云尔。则岂非大害乎。治道亦然。三代尽美矣。汉唐宋则苟合苟完苟美也。故曰治非三代。皆苟矣。一苟字而用处不同。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卑者苟字意也。尽力者尽美之意也。沟洫政治之粗处。而犹且如此。则而况于教化之本乎。愿于苟字上。 深加辨别而省察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体念焉。泰亿曰。司书推演言外之意。所达极好。若一以
三代之教。何以加焉。然民之从之者。什不一二焉。言语末也。以言语感人。其效浅矣。况以命令驱人。人谁从之。欲行其令者。须以正身为主。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故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治国平天下。皆本于此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公子荆居室注曰。聊且属循序。粗略属有节。不欲速属循序。不尽美属有节。苟字则含包两意。而以最初一苟字观之。则见其不尽美之意。合三苟字而观之。则见其不欲速之意矣。 下答曰。然矣。臣又曰。骄吝奢侈之戒。宾客所达。缕缕详悉。臣不赘陈。而第苟字用处各别。用之于居室什物之间。则苟是好个字。用之于身心学问之际。则为不好个字。学问者若以聊且粗略为安。而曰斯亦足矣云尔。则岂非大害乎。治道亦然。三代尽美矣。汉唐宋则苟合苟完苟美也。故曰治非三代。皆苟矣。一苟字而用处不同。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卑者苟字意也。尽力者尽美之意也。沟洫政治之粗处。而犹且如此。则而况于教化之本乎。愿于苟字上。 深加辨别而省察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体念焉。泰亿曰。司书推演言外之意。所达极好。若一以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9H 页
 苟字为务。而用之于学问政治之间。则无求进造极之路。其所陈戒言甚切要。愿各别 留念焉。 下答曰。当着念而勿忘矣。臣又论庶富教曰。舜之命禹曰。后非众。罔与守邦。盖欲其庶之也。其命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其命后稷曰。黎民阻饥。播时百谷。盖欲其富之也。其命契曰。敬敷五教。盖欲其教之也。礼记王制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然后兴学。无旷土则庶矣。食节则富矣。此亦庶富而教也。自古为治之道。何尝外庶富教三字也。然以设施次第言之。则教在庶富之后。以王道所重言之。则教在庶富之先。不富之弊则至于饿死。不教之弊则近于禽兽。饿死则犹可。禽兽则不可。冉有若问三者之轻重。则孔子必以教字为重。观于答子贡兵食信之教而可知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集注三代以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曰。孔子谓子产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之。三代以下。如子产之为母者。亦不可多得。况可望于师教乎。汉明帝,唐太宗能有意于师教。其意则固美矣。然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欲为人师者。必先懋己学。明帝,太宗之学果可以教人乎。闾巷之间。
苟字为务。而用之于学问政治之间。则无求进造极之路。其所陈戒言甚切要。愿各别 留念焉。 下答曰。当着念而勿忘矣。臣又论庶富教曰。舜之命禹曰。后非众。罔与守邦。盖欲其庶之也。其命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其命后稷曰。黎民阻饥。播时百谷。盖欲其富之也。其命契曰。敬敷五教。盖欲其教之也。礼记王制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然后兴学。无旷土则庶矣。食节则富矣。此亦庶富而教也。自古为治之道。何尝外庶富教三字也。然以设施次第言之。则教在庶富之后。以王道所重言之。则教在庶富之先。不富之弊则至于饿死。不教之弊则近于禽兽。饿死则犹可。禽兽则不可。冉有若问三者之轻重。则孔子必以教字为重。观于答子贡兵食信之教而可知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臣又论集注三代以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曰。孔子谓子产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之。三代以下。如子产之为母者。亦不可多得。况可望于师教乎。汉明帝,唐太宗能有意于师教。其意则固美矣。然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欲为人师者。必先懋己学。明帝,太宗之学果可以教人乎。闾巷之间。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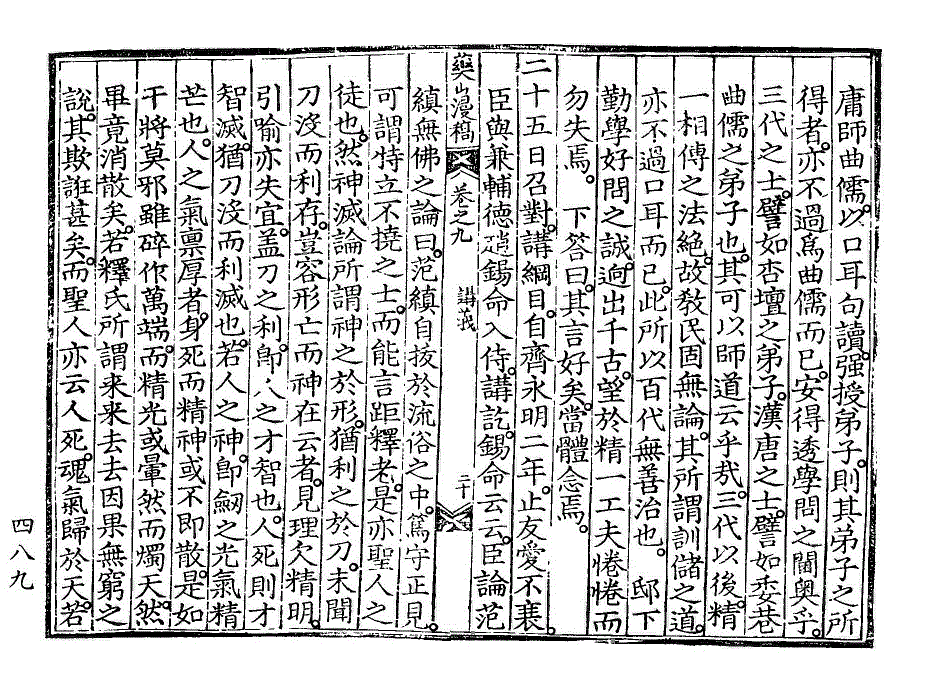 庸师曲儒。以口耳句读。强授弟子。则其弟子之所得者。亦不过为曲儒而已。安得透学问之阃奥乎。三代之士。譬如杏坛之弟子。汉唐之士。譬如委巷曲儒之弟子也。其可以师道云乎哉。三代以后。精一相传之法绝。故教民固无论。其所谓训储之道。亦不过口耳而已。此所以百代无善治也。 邸下勤学好问之诚。迥出千古。望于精一工夫惓惓而勿失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体念焉。
庸师曲儒。以口耳句读。强授弟子。则其弟子之所得者。亦不过为曲儒而已。安得透学问之阃奥乎。三代之士。譬如杏坛之弟子。汉唐之士。譬如委巷曲儒之弟子也。其可以师道云乎哉。三代以后。精一相传之法绝。故教民固无论。其所谓训储之道。亦不过口耳而已。此所以百代无善治也。 邸下勤学好问之诚。迥出千古。望于精一工夫惓惓而勿失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体念焉。二十五日召对。讲纲目。自齐永明二年。止友爱不衰。臣与兼辅德赵锡命入侍。讲讫。锡命云云。臣论范缜无佛之论曰。范缜自拔于流俗之中。笃守正见。可谓特立不挠之士。而能言距释老。是亦圣人之徒也。然神灭论所谓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云者。见理欠精明。引喻亦失宜。盖刀之利。即人之才智也。人死则才智灭。犹刀没而利灭也。若人之神。即剑之光气精芒也。人之气禀厚者。身死而精神或不即散。是如干将莫邪虽碎作万端。而精光或晕然而烛天。然毕竟消散矣。若释氏所谓来来去去因果无穷之说。其欺诳甚矣。而圣人亦云人死。魂气归于天。若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0H 页
 刀之利。则与刀俱没。若谓之利。归于某处。则不成说矣。其不可以形之神。譬刀之利者明矣。 下答曰。所见明矣。臣又论文惠太子东田观穫曰。太子生于深宫。长于富贵。岂知盘中之飧粒粒皆辛苦乎。故周公作无逸书,七月诗以戒成王。所以基成周八百年基业也。今文惠之观穫。不过出于游观之意。而众皆唯唯。则左右前后。皆匪人也。独范云之言。可谓切挚。而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哉。为人君之适嗣者。所乏者非富贵也。楼馆壮丽。示富贵容。何益于太子哉。不过聚谤于一时。贻讥于百代矣。愿以文惠太子为戒。而以范云之言为法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体念焉。
刀之利。则与刀俱没。若谓之利。归于某处。则不成说矣。其不可以形之神。譬刀之利者明矣。 下答曰。所见明矣。臣又论文惠太子东田观穫曰。太子生于深宫。长于富贵。岂知盘中之飧粒粒皆辛苦乎。故周公作无逸书,七月诗以戒成王。所以基成周八百年基业也。今文惠之观穫。不过出于游观之意。而众皆唯唯。则左右前后。皆匪人也。独范云之言。可谓切挚。而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哉。为人君之适嗣者。所乏者非富贵也。楼馆壮丽。示富贵容。何益于太子哉。不过聚谤于一时。贻讥于百代矣。愿以文惠太子为戒。而以范云之言为法焉。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体念焉。二十六日召对。讲纲目。自齐永明三年。止十三在河北。臣与文学李真洙入侍。讲讫。真洙云云。臣论谶纬巫卜曰。纲之特书。许之也。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八曰造言之刑。注曰。挟左道以惑民者也。谶纬巫觋及委巷巫筮。非经典所载者。皆左道也。为人上者必痛禁。然后可无惑世诬民之弊。此魏之善政也。 下答曰。然矣。臣又论王俭好礼学春秋。衣冠翕然。更尚儒术曰。夫经学者。非所以资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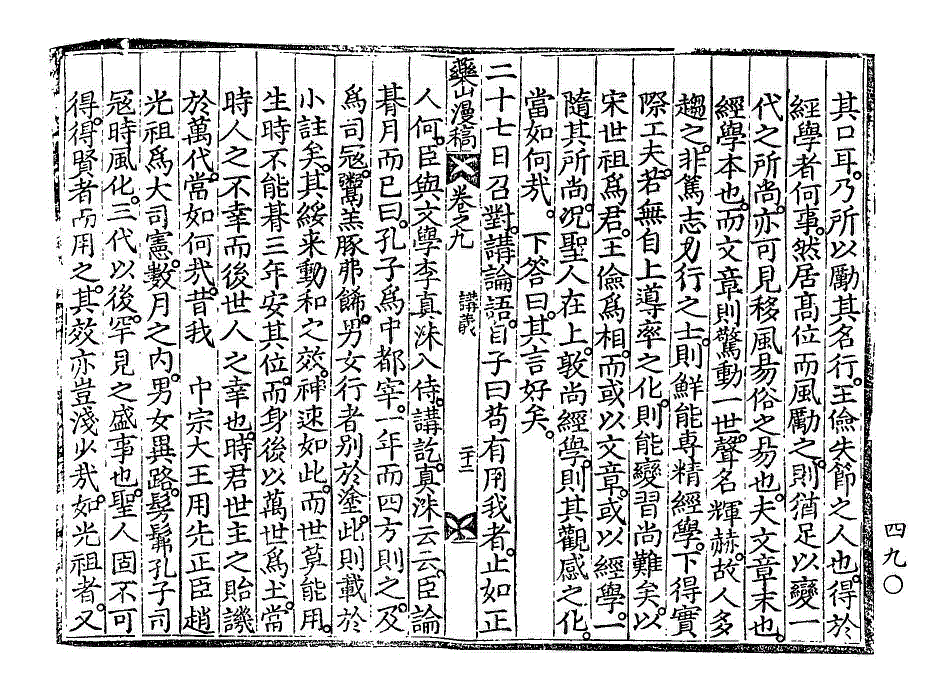 其口耳。乃所以励其名行。王俭失节之人也。得于经学者何事。然居高位而风励之。则犹足以变一代之所尚。亦可见移风易俗之易也。夫文章末也。经学本也。而文章则惊动一世。声名辉赫。故人多趋之。非笃志力行之士。则鲜能专精经学。下得实际工夫。若无自上导率之化。则能变习尚难矣。以宋世祖为君。王俭为相。而或以文章。或以经学。一随其所尚。况圣人在上。敦尚经学。则其观感之化。当如何哉。 下答曰。其言好矣。
其口耳。乃所以励其名行。王俭失节之人也。得于经学者何事。然居高位而风励之。则犹足以变一代之所尚。亦可见移风易俗之易也。夫文章末也。经学本也。而文章则惊动一世。声名辉赫。故人多趋之。非笃志力行之士。则鲜能专精经学。下得实际工夫。若无自上导率之化。则能变习尚难矣。以宋世祖为君。王俭为相。而或以文章。或以经学。一随其所尚。况圣人在上。敦尚经学。则其观感之化。当如何哉。 下答曰。其言好矣。二十七日召对。讲论语。自子曰苟有用我者。止如正人何。臣与文学李真洙入侍。讲讫。真洙云云。臣论期月而已曰。孔子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则之。及为司寇。鬻羔豚弗饰。男女行者别于涂。此则载于小注矣。其绥来动和之效。神速如此。而世莫能用。生时不能期三年安其位。而身后以万世为土。当时人之不幸而后世人之幸也。时君世主之贻讥于万代。当如何哉。昔我 中宗大王用先正臣赵光祖为大司宪。数月之内。男女异路。髣髴孔子司寇时风化。三代以后。罕见之盛事也。圣人固不可得。得贤者而用之。其效亦岂浅少哉。如光祖者。又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1H 页
 不可得。而代不乏人。未尝有有君而无臣者矣。心诚求之。必有了一代之事而做一代之治者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
不可得。而代不乏人。未尝有有君而无臣者矣。心诚求之。必有了一代之事而做一代之治者矣。 下答曰。其言好矣。二十八日夜对。讲纲目。自齐永明五年。止民不困。臣与文学李真洙入侍。讲讫。真洙云云。臣论魏出宫人罢末作曰。魏孝文不幸出于夷狄。其天资则甚高。求之汉唐宋。实难多得如此等事。虽谓之盛德事可也。夷狄之君。尚能崇俭斥奢。不作无益。若我朝则当以三代自期。而未能革奢侈之风。甚可愧也。以有用之银货。易北京无用之锦绣。倡优下贱。皆服异国之珍奇。其所耗费。奚特尚方末作之弊而已。我国土产䌷木布。足以供公私之用。何必贸易于彼国而用之哉。此弊亦不可不革矣。昔我 成宗大王于寝疾中。引接臣僚卧内。所覆只是欲弊䌷衾及茶褐而已。至今称颂。传以为美谈。伏望每读史传。至古帝王崇俭处。则必须引类提醒。远追三代俭朴之治。近体 列祖清素之德。念玆在玆。罔或少忽。 下答曰。其言好矣。当体念焉。臣论魏高宗谓群臣曰。朕始学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日思之。岂惟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1L 页
 曰。观此魏主之语。则勤学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学问不可不趁其时节。失其时节。则虽悔莫及。魏主夷狄之主。而能知学问之为重。痛自刻责。可谓空谷跫音也。即今师在外傅未差。会讲日次。每每颐禀。诚为可惜。而 邸下春秋鼎盛。异于冲年。岂待师傅之教谕而后自勉也哉。向日三伏苦热。犹不辍筵。从今秋凉渐生。想必益加勤孜。而 邸下学问高明。与幼冲时讲读不同。当以所讲处句句字字。着落身心上用工。不可以逐日趁课为极功也。臣之入侍讲筵。亦已多日矣。每于入侍时。日势抵暮。开讲已久。而未尝见 邸下少有怠弛之色。 邸下勤学之诚。臣实感叹。而 邸下深宫之中燕閒之时。则臣不能入侍。臣未知 邸下之俨庄勤懋。亦如开讲时乎。于是而少有勤忽。不加省察。则其根柢潜藏。萌蘖暗长。将使 清明刚健之体。日消于不知不觉之中矣。人皆知骄侈淫荒。显然放肆。为天理之贼。而不知隐微之中。纤毫之累。皆足为天理之贼也。可不惧哉。故大学一篇。以慎独为重。中庸一篇。以不愧屋漏为重。伏望于此而 深加省察焉。 下答曰。其言切实。当体念而勿忘
曰。观此魏主之语。则勤学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学问不可不趁其时节。失其时节。则虽悔莫及。魏主夷狄之主。而能知学问之为重。痛自刻责。可谓空谷跫音也。即今师在外傅未差。会讲日次。每每颐禀。诚为可惜。而 邸下春秋鼎盛。异于冲年。岂待师傅之教谕而后自勉也哉。向日三伏苦热。犹不辍筵。从今秋凉渐生。想必益加勤孜。而 邸下学问高明。与幼冲时讲读不同。当以所讲处句句字字。着落身心上用工。不可以逐日趁课为极功也。臣之入侍讲筵。亦已多日矣。每于入侍时。日势抵暮。开讲已久。而未尝见 邸下少有怠弛之色。 邸下勤学之诚。臣实感叹。而 邸下深宫之中燕閒之时。则臣不能入侍。臣未知 邸下之俨庄勤懋。亦如开讲时乎。于是而少有勤忽。不加省察。则其根柢潜藏。萌蘖暗长。将使 清明刚健之体。日消于不知不觉之中矣。人皆知骄侈淫荒。显然放肆。为天理之贼。而不知隐微之中。纤毫之累。皆足为天理之贼也。可不惧哉。故大学一篇。以慎独为重。中庸一篇。以不愧屋漏为重。伏望于此而 深加省察焉。 下答曰。其言切实。当体念而勿忘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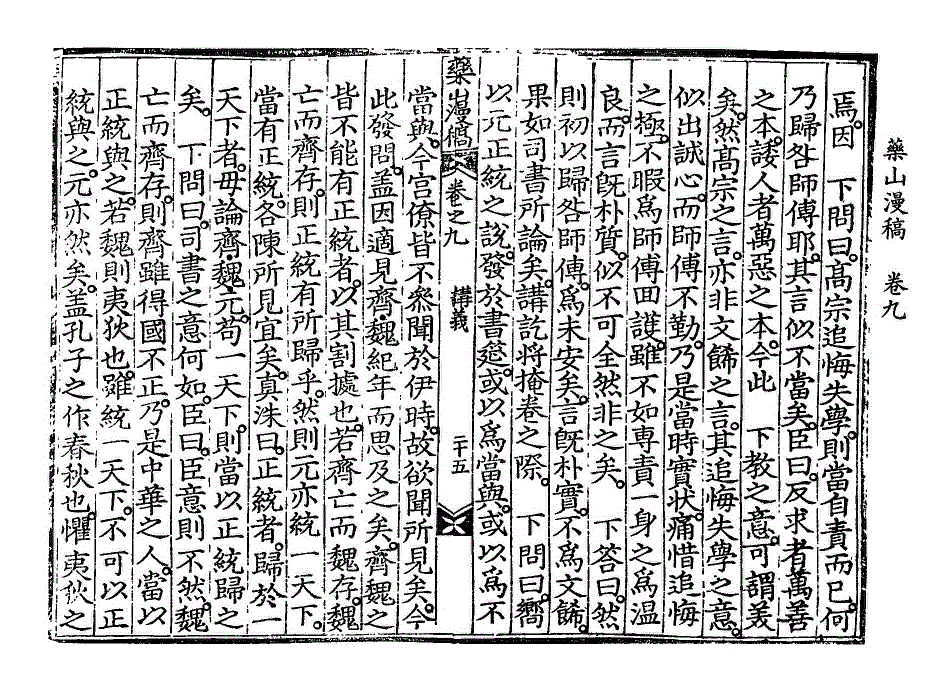 焉。因 下问曰。高宗追悔失学。则当自责而已。何乃归咎师傅耶。其言似不当矣。臣曰。反求者万善之本。诿人者万恶之本。今此 下教之意。可谓美矣。然高宗之言。亦非文饰之言。其追悔失学之意。似出诚心。而师傅不勤。乃是当时实状。痛惜追悔之极。不暇为师傅回护。虽不如专责一身之为温良。而言既朴质。似不可全然非之矣。 下答曰。然则初以归咎师傅。为未安矣。言既朴实。不为文饰。果如司书所论矣。讲讫将掩卷之际。 下问曰。向以元正统之说。发于书筵。或以为当与。或以为不当与。今宫僚皆不参闻于伊时。故欲闻所见矣。今此发问。盖因适见齐,魏纪年而思及之矣。齐魏之皆不能有正统者。以其割据也。若齐亡而魏存。魏亡而齐存。则正统有所归乎。然则元亦统一天下。当有正统。各陈所见宜矣。真洙曰。正统者。归于一天下者。毋论齐,魏,元。苟一天下。则当以正统归之矣。 下问曰。司书之意何如。臣曰。臣意则不然。魏亡而齐存。则齐虽得国不正。乃是中华之人。当以正统与之。若魏则夷狄也。虽统一天下。不可以正统与之。元亦然矣。盖孔子之作春秋也。惧夷狄之
焉。因 下问曰。高宗追悔失学。则当自责而已。何乃归咎师傅耶。其言似不当矣。臣曰。反求者万善之本。诿人者万恶之本。今此 下教之意。可谓美矣。然高宗之言。亦非文饰之言。其追悔失学之意。似出诚心。而师傅不勤。乃是当时实状。痛惜追悔之极。不暇为师傅回护。虽不如专责一身之为温良。而言既朴质。似不可全然非之矣。 下答曰。然则初以归咎师傅。为未安矣。言既朴实。不为文饰。果如司书所论矣。讲讫将掩卷之际。 下问曰。向以元正统之说。发于书筵。或以为当与。或以为不当与。今宫僚皆不参闻于伊时。故欲闻所见矣。今此发问。盖因适见齐,魏纪年而思及之矣。齐魏之皆不能有正统者。以其割据也。若齐亡而魏存。魏亡而齐存。则正统有所归乎。然则元亦统一天下。当有正统。各陈所见宜矣。真洙曰。正统者。归于一天下者。毋论齐,魏,元。苟一天下。则当以正统归之矣。 下问曰。司书之意何如。臣曰。臣意则不然。魏亡而齐存。则齐虽得国不正。乃是中华之人。当以正统与之。若魏则夷狄也。虽统一天下。不可以正统与之。元亦然矣。盖孔子之作春秋也。惧夷狄之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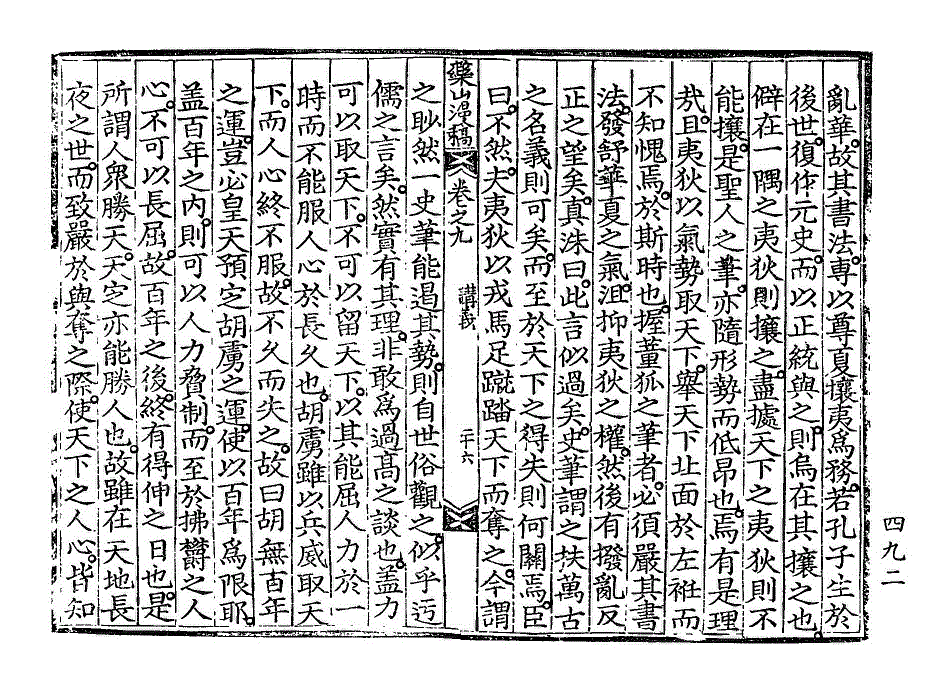 乱华。故其书法。专以尊夏攘夷为务。若孔子生于后世。复作元史。而以正统与之。则乌在其攘之也。僻在一隅之夷狄则攘之。尽据天下之夷狄则不能攘。是圣人之笔。亦随形势而低昂也。焉有是理哉。且夷狄以气势取天下。举天下北面于左衽而不知愧焉。于斯时也。握蕫狐之笔者。必须严其书法。发舒华夏之气。沮抑夷狄之权。然后有拨乱反正之望矣。真洙曰。此言似过矣。史笔谓之扶万古之名义则可矣。而至于天下之得失则何关焉。臣曰。不然。夫夷狄以戎马足蹴踏天下而夺之。今谓之眇然一史笔能遏其势。则自世俗观之。似乎迂儒之言矣。然实有其理。非敢为过高之谈也。盖力可以取天下。不可以留天下。以其能屈人力于一时而不能服人心于长久也。胡虏虽以兵威取天下。而人心终不服。故不久而失之。故曰胡无百年之运。岂必皇天预定胡虏之运。使以百年为限耶。盖百年之内。则可以人力䝱制。而至于拂郁之人心。不可以长屈。故百年之后。终有得伸之日也。是所谓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也。故虽在天地长夜之世。而致严于与夺之际。使天下之人心。皆知
乱华。故其书法。专以尊夏攘夷为务。若孔子生于后世。复作元史。而以正统与之。则乌在其攘之也。僻在一隅之夷狄则攘之。尽据天下之夷狄则不能攘。是圣人之笔。亦随形势而低昂也。焉有是理哉。且夷狄以气势取天下。举天下北面于左衽而不知愧焉。于斯时也。握蕫狐之笔者。必须严其书法。发舒华夏之气。沮抑夷狄之权。然后有拨乱反正之望矣。真洙曰。此言似过矣。史笔谓之扶万古之名义则可矣。而至于天下之得失则何关焉。臣曰。不然。夫夷狄以戎马足蹴踏天下而夺之。今谓之眇然一史笔能遏其势。则自世俗观之。似乎迂儒之言矣。然实有其理。非敢为过高之谈也。盖力可以取天下。不可以留天下。以其能屈人力于一时而不能服人心于长久也。胡虏虽以兵威取天下。而人心终不服。故不久而失之。故曰胡无百年之运。岂必皇天预定胡虏之运。使以百年为限耶。盖百年之内。则可以人力䝱制。而至于拂郁之人心。不可以长屈。故百年之后。终有得伸之日也。是所谓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也。故虽在天地长夜之世。而致严于与夺之际。使天下之人心。皆知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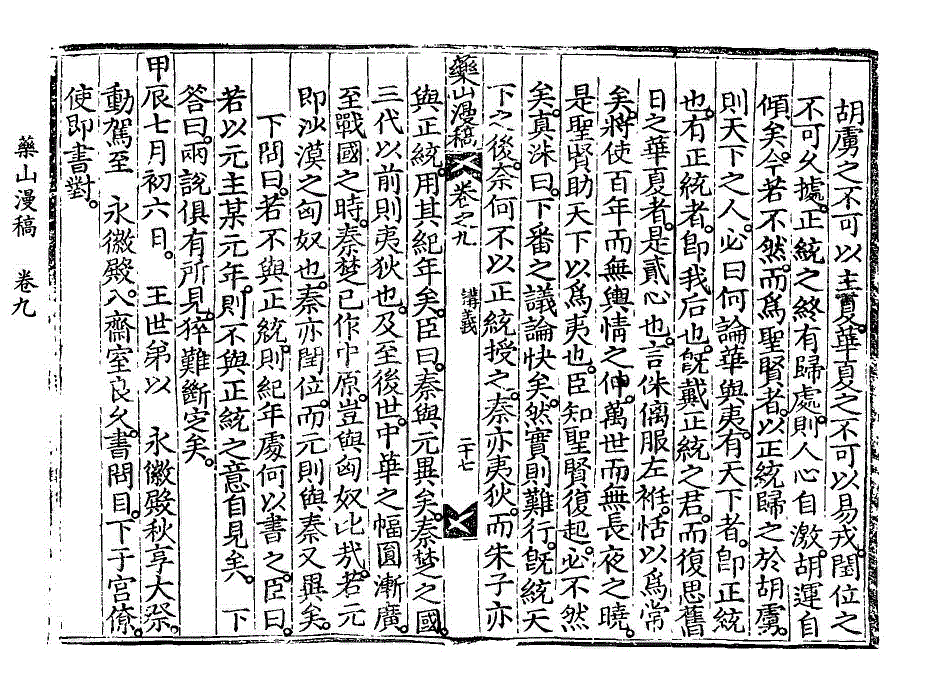 胡虏之不可以主夏。华夏之不可以易戎。闰位之不可久据。正统之终有归处。则人心自激。胡运自倾矣。今若不然。而为圣贤者。以正统归之于胡虏。则天下之人。必曰何论华与夷。有天下者。即正统也。有正统者。即我后也。既戴正统之君。而复思旧日之华夏者。是贰心也。言侏俪服左衽。恬以为常矣。将使百年而无舆情之伸。万世而无长夜之晓。是圣贤助天下以为夷也。臣知圣贤复起。必不然矣。真洙曰。下番之议论快矣。然实则难行。既统天下之后。奈何不以正统授之。秦亦夷狄。而朱子亦与正统。用其纪年矣。臣曰。秦与元异矣。秦楚之国。三代以前则夷狄也。及至后世。中华之幅圆渐广。至战国之时。秦楚已作中原。岂与匈奴比哉。若元即沙漠之匈奴也。秦亦闰位。而元则与秦又异矣。 下问曰。若不与正统。则纪年处何以书之。臣曰。若以元主某元年。则不与正统之意自见矣。 下答曰。两说俱有所见。猝难断定矣。
胡虏之不可以主夏。华夏之不可以易戎。闰位之不可久据。正统之终有归处。则人心自激。胡运自倾矣。今若不然。而为圣贤者。以正统归之于胡虏。则天下之人。必曰何论华与夷。有天下者。即正统也。有正统者。即我后也。既戴正统之君。而复思旧日之华夏者。是贰心也。言侏俪服左衽。恬以为常矣。将使百年而无舆情之伸。万世而无长夜之晓。是圣贤助天下以为夷也。臣知圣贤复起。必不然矣。真洙曰。下番之议论快矣。然实则难行。既统天下之后。奈何不以正统授之。秦亦夷狄。而朱子亦与正统。用其纪年矣。臣曰。秦与元异矣。秦楚之国。三代以前则夷狄也。及至后世。中华之幅圆渐广。至战国之时。秦楚已作中原。岂与匈奴比哉。若元即沙漠之匈奴也。秦亦闰位。而元则与秦又异矣。 下问曰。若不与正统。则纪年处何以书之。臣曰。若以元主某元年。则不与正统之意自见矣。 下答曰。两说俱有所见。猝难断定矣。七月
初六日。 王世弟以 永徽殿秋享大祭。动驾至 永徽殿。入斋室良久。书问目。下于宫僚。使即书对。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3L 页
 大学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程子视箴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工夫次第之或先或后何耶。颜子以上智之资。判于理欲之际。故不复疑问。直请其目。谓初学则心不正而能制外乎。又或问中朱子曰。制却在内。集注中亦曰。是人心之所以为主。又曰。自外而内。自叶流根之意。若学者将用力于此。下工何先。 下令曰。自大学至或先或后何耶。
大学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程子视箴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工夫次第之或先或后何耶。颜子以上智之资。判于理欲之际。故不复疑问。直请其目。谓初学则心不正而能制外乎。又或问中朱子曰。制却在内。集注中亦曰。是人心之所以为主。又曰。自外而内。自叶流根之意。若学者将用力于此。下工何先。 下令曰。自大学至或先或后何耶。大学之说。似从内面做去。程子之箴。似从外面做去。而圣贤之训。该本末兼动静。初何尝异也。朱子曰。学者之病。只得说得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词气。往往全不加功。设使存得。亦与释老何异。又况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由此观之。则大学之所谓正心者。何尝放过于容貌词气之间。而用工于块然恍然之地。如释老之学乎。正心在主敬。敬只是心惺惺法。然不整齐严肃而能惺惺者。未之有也。曾子正终曰。容貌颜色辞气而已。成王顾命曰。思夫人自乱于威仪。由此观之。则正心工夫。下手处可知也。正衣冠尊瞻视俨若思时。非僻何自以入焉。正心之训。制外之说。未尝有二也。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4H 页
 下令曰。自颜子。至能制外乎。
下令曰。自颜子。至能制外乎。邸下若有疑于颜子造诣已高。过了正心阶级。故孔子只说与四勿。不复提及于正心工夫者。而窃恐有不然者。虽以尧舜之圣。而所传者不过人心道心之辨。人心道心。即理欲之际也。岂于精一之外。复有制外工夫乎。西山真氏曰。孔子之所谓己。即舜之所谓人心。孔子之所谓礼。即舜之所谓道心。然则克复即正心工夫。精一包得制外工夫。岂可以正心为制外前基址。以制外为正心后层级乎。不惟不可分先后。亦不可分内外。洪范五事。曰貌言,视,听,思。而孔子之教。则视,听,言,动而已。思不与焉何哉。勿之为言。禁止之谓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动。非心为之主宰。其孰能禁之。然则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四勿虽不及思字。而思字自在于四勿之中矣。制外正心。即是括动静彻上下底工夫。岂有内外之异。而又岂有上智初学之别乎。
下令曰。自或问。至流根意。
程子曰。闲邪更著甚工夫。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这敬依据下手处。从容貌辞气始而心自正。此所谓自叶流根之意也。然则四勿何尝非
药山漫稿卷之九 第 494L 页
 里面工夫耶。
里面工夫耶。下令曰。自若学者。至何先。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朱子曰。敬主于中。义防于外。二者夹持。要放下霎然不得。敬者所以直内。而其下手处。在容貌辞气。义者所以方外。而告子以为外。则亚圣严斥之。盖敬非容貌辞气。无所依据。而容貌辞气非慎独。则为外饰而已。方其未与物接。视听不动之时。齐庄俨若气象可想。夫岂如释老之置心空荡。俗学之妇人捡押乎。大抵下工处。以敬为先。敬以容貌辞气为先。容貌辞气。以俨若思为主。敬内也。容貌辞气外也。俨若思又内也。才说内外先后。窃恐堕落一边矣。
药山漫稿卷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