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x 页
戒惧庵集卷之三
书
书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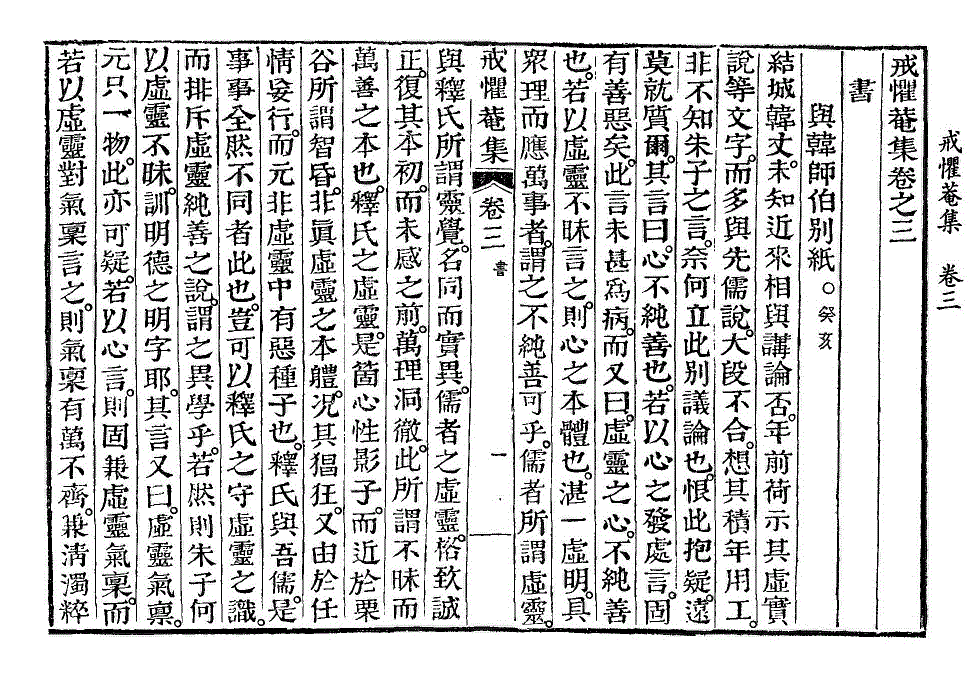 与韩师伯别纸(癸亥)
与韩师伯别纸(癸亥)结城韩丈。未知近来相与讲论否。年前荷示其虚实说等文字。而多与先儒说。大段不合。想其积年用工。非不知朱子之言。奈何立此别议论也。恨此抱疑。远莫就质尔。其言曰。心不纯善也。若以心之发处言。固有善恶矣。此言未甚为病。而又曰。虚灵之心。不纯善也。若以虚灵不昧言之。则心之本体也。湛一虚明。具众理而应万事者。谓之不纯善可乎。儒者所谓虚灵。与释氏所谓灵觉。名同而实异。儒者之虚灵。格致诚正。复其本初。而未感之前。万理洞彻。此所谓不昧而万善之本也。释氏之虚灵。是个心性影子。而近于栗谷所谓智昏。非真虚灵之本体。况其猖狂。又由于任情妄行。而元非虚灵中有恶种子也。释氏与吾儒。是事事全然不同者此也。岂可以释氏之守虚灵之识。而排斥虚灵纯善之说。谓之异学乎。若然则朱子何以虚灵不昧。训明德之明字耶。其言又曰。虚灵气禀。元只一物。此亦可疑。若以心言。则固兼虚灵气禀。而若以虚灵对气禀言之。则气禀有万不齐。兼清浊粹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4L 页
 驳也。虚灵。是乃气之极精爽处。极其清而纯乎善也。故朱子释大学章句。先言虚灵不昧。而后言为气禀所拘。若是其分别言之。岂可混一而称也。韩丈以虚灵气禀。看做一样。故未发虚明之时。谓有清浊美恶之本色。而虚灵之心不纯善也。盖其病根。都在于混沦看虚灵气禀故也。虽然。此不成义理。故其言前后矛盾。左右错乱。夫既曰湛一虚明未发也。清浊美恶气禀也。又曰。未发之前。气禀本色自在。夫未发之前。湛一虚明。则浊本色。何处并立耶。浊本色自在。则其能湛一虚明耶。此其矛盾者也。既曰气之精爽。聚于人而为虚灵。又曰。众人浊气聚而虚灵。夫精爽。即极清之气也。浊气亦可谓精爽乎。气浊而果能虚灵乎。窃谓虚灵不昧。虽涉乎气。而即人生而静。湛一虚明之心。张子所谓湛一气之本也。于此决不可谓带些浊气也。未发。是个复其虚灵不昧之本初。而子思直谓之中。朱子又谓之性。于此决不可谓夹杂了浊本色也。圣人之常觉于理者。以其合下清粹。全此虚灵而无所昏蔽者也。众人之常觉于欲者。以其初虽虚灵。而气禀所拘。有时而昏者也。非以虚灵之本体不能皆善也。然虚灵之本体。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能
驳也。虚灵。是乃气之极精爽处。极其清而纯乎善也。故朱子释大学章句。先言虚灵不昧。而后言为气禀所拘。若是其分别言之。岂可混一而称也。韩丈以虚灵气禀。看做一样。故未发虚明之时。谓有清浊美恶之本色。而虚灵之心不纯善也。盖其病根。都在于混沦看虚灵气禀故也。虽然。此不成义理。故其言前后矛盾。左右错乱。夫既曰湛一虚明未发也。清浊美恶气禀也。又曰。未发之前。气禀本色自在。夫未发之前。湛一虚明。则浊本色。何处并立耶。浊本色自在。则其能湛一虚明耶。此其矛盾者也。既曰气之精爽。聚于人而为虚灵。又曰。众人浊气聚而虚灵。夫精爽。即极清之气也。浊气亦可谓精爽乎。气浊而果能虚灵乎。窃谓虚灵不昧。虽涉乎气。而即人生而静。湛一虚明之心。张子所谓湛一气之本也。于此决不可谓带些浊气也。未发。是个复其虚灵不昧之本初。而子思直谓之中。朱子又谓之性。于此决不可谓夹杂了浊本色也。圣人之常觉于理者。以其合下清粹。全此虚灵而无所昏蔽者也。众人之常觉于欲者。以其初虽虚灵。而气禀所拘。有时而昏者也。非以虚灵之本体不能皆善也。然虚灵之本体。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能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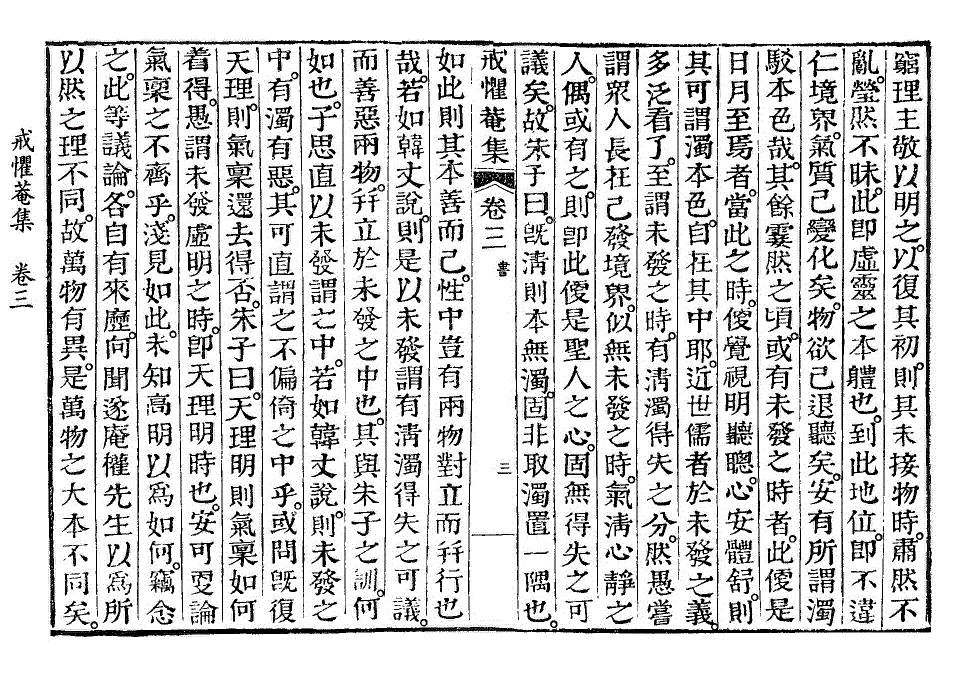 穷理主敬以明之。以复其初。则其未接物时。肃然不乱。莹然不昧。此即虚灵之本体也。到此地位。即不违仁境界。气质已变化矣。物欲已退听矣。安有所谓浊驳本色哉。其馀霎然之顷。或有未发之时者。此便是日月至焉者。当此之时。便觉视明听聪。心安体舒。则其可谓浊本色。自在其中耶。近世儒者于未发之义。多泛看了。至谓未发之时。有清浊得失之分。然愚尝谓众人长在已发境界。似无未发之时。气清心静之人。偶或有之。则即此便是圣人之心。固无得失之可议矣。故朱子曰。既清则本无浊。固非取浊置一隅也。如此则其本善而已。性中岂有两物对立而并行也哉。若如韩丈说。则是以未发谓有清浊得失之可议。而善恶两物。并立于未发之中也。其与朱子之训。何如也。子思直以未发谓之中。若如韩丈说。则未发之中。有浊有恶。其可直谓之不偏倚之中乎。或问既复天理。则气禀还去得否。朱子曰。天理明则气禀如何着得。愚谓未发虚明之时。即天理明时也。安可更论气禀之不齐乎。浅见如此。未知高明以为如何。窃念之。此等议论。各自有来历。向闻遂庵权先生以为所以然之理不同。故万物有异。是万物之大本不同矣。
穷理主敬以明之。以复其初。则其未接物时。肃然不乱。莹然不昧。此即虚灵之本体也。到此地位。即不违仁境界。气质已变化矣。物欲已退听矣。安有所谓浊驳本色哉。其馀霎然之顷。或有未发之时者。此便是日月至焉者。当此之时。便觉视明听聪。心安体舒。则其可谓浊本色。自在其中耶。近世儒者于未发之义。多泛看了。至谓未发之时。有清浊得失之分。然愚尝谓众人长在已发境界。似无未发之时。气清心静之人。偶或有之。则即此便是圣人之心。固无得失之可议矣。故朱子曰。既清则本无浊。固非取浊置一隅也。如此则其本善而已。性中岂有两物对立而并行也哉。若如韩丈说。则是以未发谓有清浊得失之可议。而善恶两物。并立于未发之中也。其与朱子之训。何如也。子思直以未发谓之中。若如韩丈说。则未发之中。有浊有恶。其可直谓之不偏倚之中乎。或问既复天理。则气禀还去得否。朱子曰。天理明则气禀如何着得。愚谓未发虚明之时。即天理明时也。安可更论气禀之不齐乎。浅见如此。未知高明以为如何。窃念之。此等议论。各自有来历。向闻遂庵权先生以为所以然之理不同。故万物有异。是万物之大本不同矣。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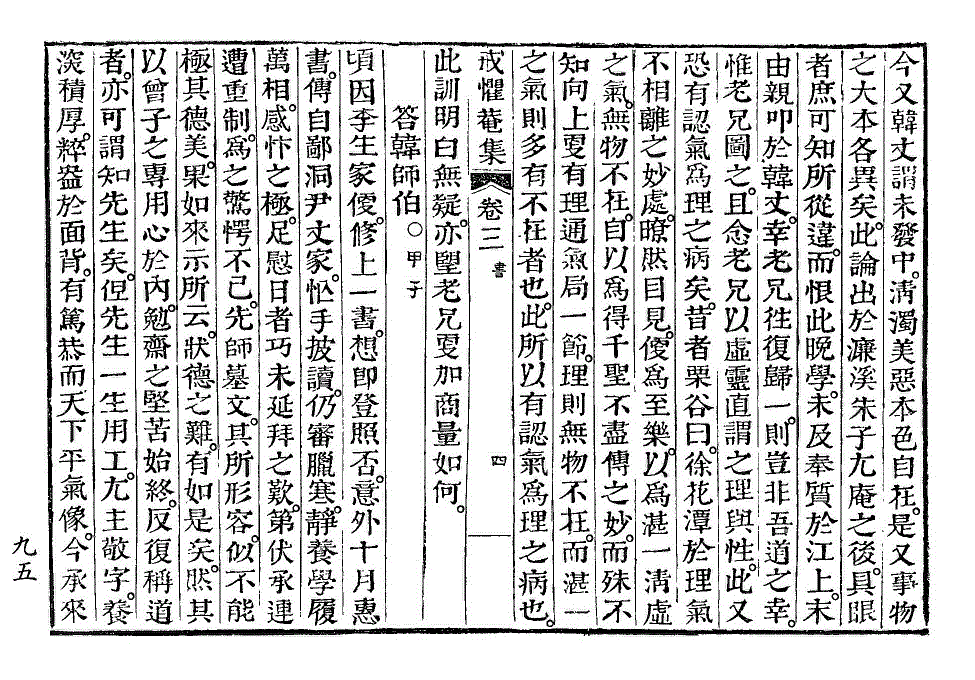 今又韩丈谓未发中。清浊美恶本色自在。是又事物之大本各异矣。此论出于濂溪朱子尤庵之后。具眼者庶可知所从违。而恨此晚学。未及奉质于江上。末由亲叩于韩丈。幸老兄往复归一。则岂非吾道之幸。惟老兄图之。且念老兄以虚灵直谓之理与性。此又恐有认气为理之病矣。昔者栗谷曰。徐花潭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暸然目见。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此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此训明白无疑。亦望老兄更加商量如何。
今又韩丈谓未发中。清浊美恶本色自在。是又事物之大本各异矣。此论出于濂溪朱子尤庵之后。具眼者庶可知所从违。而恨此晚学。未及奉质于江上。末由亲叩于韩丈。幸老兄往复归一。则岂非吾道之幸。惟老兄图之。且念老兄以虚灵直谓之理与性。此又恐有认气为理之病矣。昔者栗谷曰。徐花潭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暸然目见。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此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此训明白无疑。亦望老兄更加商量如何。答韩师伯(甲子)
顷因李生家便。修上一书。想即登照否。意外十月惠书。传自鄙洞尹丈家。忙手披读。仍审腊寒。静养学履万相。感忭之极。足慰日者巧未延拜之叹。第伏承连遭重制。为之惊愕不已。先师墓文。其所形容。似不能极其德美。果如来示所云。状德之难。有如是矣。然其以曾子之专用心于内。勉斋之坚苦始终。反复称道者。亦可谓知先生矣。但先生一生用工。尤主敬字。养深积厚。粹盎于面背。有笃恭而天下平气像。今承来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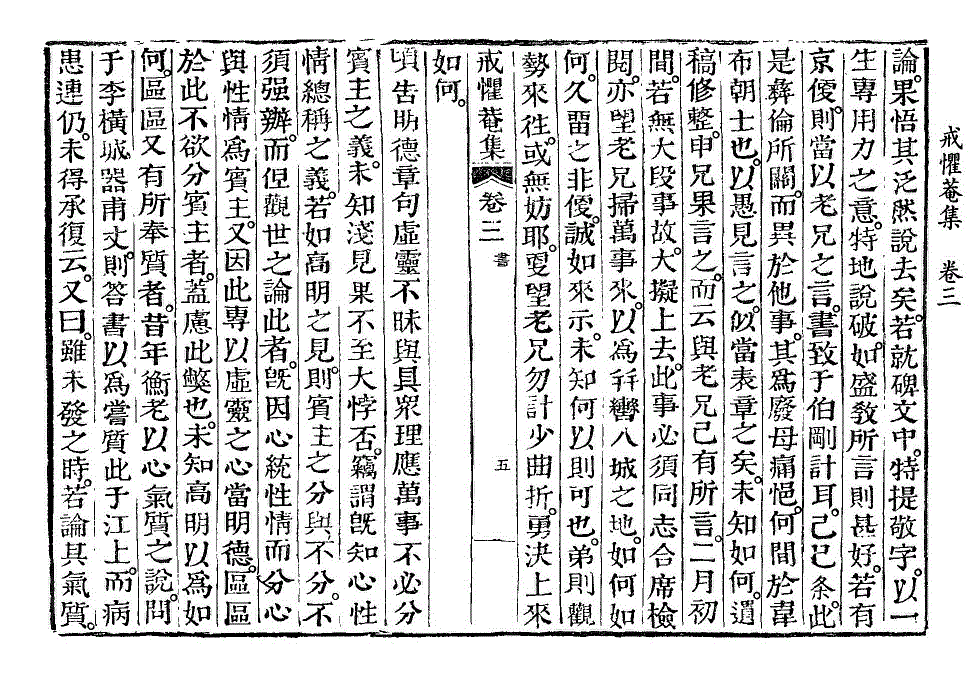 论。果悟其泛然说去矣。若就碑文中。特提敬字。以一生专用力之意。特地说破。如盛教所言则甚好。若有京便。则当以老兄之言。书致于伯刚计耳。己巳条。此是彝伦所关。而异于他事。其为废母痛悒。何间于韦布朝士也。以愚见言之。似当表章之矣。未知如何。遗稿修整。申兄果言之。而云与老兄已有所言。二月初间。若无大段事故。大拟上去。此事必须同志合席检阅。亦望老兄扫万事来。以为并辔入城之地。如何如何。久留之非便。诚如来示。未知何以则可也。弟则观势来往。或无妨耶。更望老兄勿计少曲折。勇决上来如何。
论。果悟其泛然说去矣。若就碑文中。特提敬字。以一生专用力之意。特地说破。如盛教所言则甚好。若有京便。则当以老兄之言。书致于伯刚计耳。己巳条。此是彝伦所关。而异于他事。其为废母痛悒。何间于韦布朝士也。以愚见言之。似当表章之矣。未知如何。遗稿修整。申兄果言之。而云与老兄已有所言。二月初间。若无大段事故。大拟上去。此事必须同志合席检阅。亦望老兄扫万事来。以为并辔入城之地。如何如何。久留之非便。诚如来示。未知何以则可也。弟则观势来往。或无妨耶。更望老兄勿计少曲折。勇决上来如何。顷告明德章句虚灵不昧与具众理应万事不必分宾主之义。未知浅见果不至大悖否。窃谓既知心性情总称之义。若如高明之见。则宾主之分与不分。不须强办。而但观世之论此者。既因心统性情而分心与性情为宾主。又因此专以虚灵之心当明德。区区于此不欲分宾主者。盖虑此弊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区区又有所奉质者。昔年衡老以心气质之说。问于李横城器甫丈。则答书以为尝质此于江上。而病患连仍。未得承复云。又曰。虽未发之时。若论其气质。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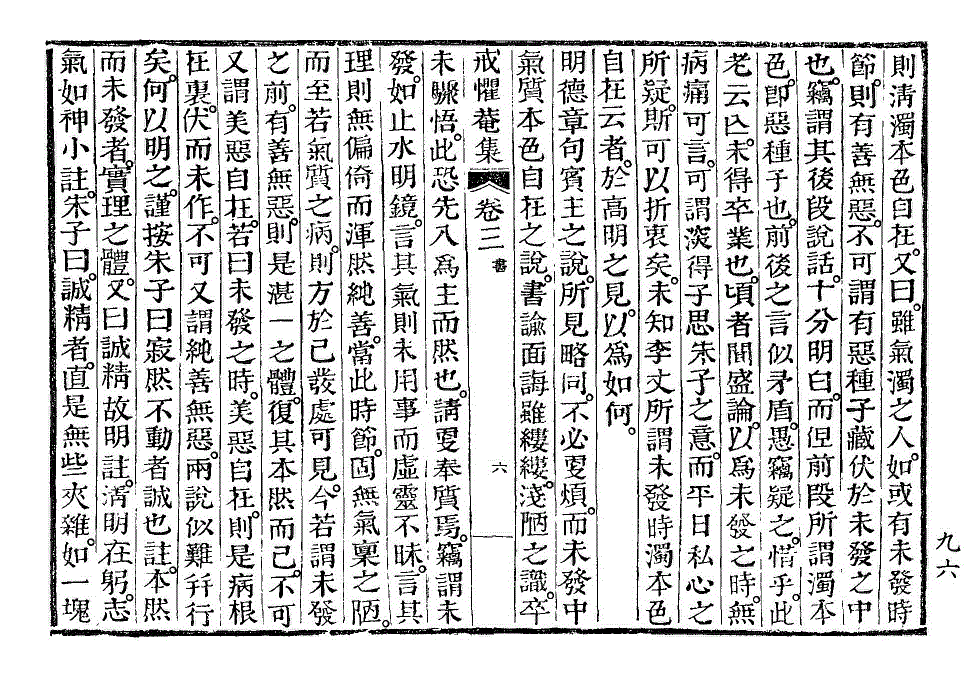 则清浊本色自在。又曰。虽气浊之人。如或有未发时节。则有善无恶。不可谓有恶种子藏伏于未发之中也。窃谓其后段说话。十分明白。而但前段所谓浊本色。即恶种子也。前后之言似矛盾。愚窃疑之。惜乎。此老云亡。未得卒业也。顷者闻盛论。以为未发之时。无病痛可言。可谓深得子思朱子之意。而平日私心之所疑。斯可以折衷矣。未知李丈所谓未发时浊本色自在云者。于高明之见。以为如何。
则清浊本色自在。又曰。虽气浊之人。如或有未发时节。则有善无恶。不可谓有恶种子藏伏于未发之中也。窃谓其后段说话。十分明白。而但前段所谓浊本色。即恶种子也。前后之言似矛盾。愚窃疑之。惜乎。此老云亡。未得卒业也。顷者闻盛论。以为未发之时。无病痛可言。可谓深得子思朱子之意。而平日私心之所疑。斯可以折衷矣。未知李丈所谓未发时浊本色自在云者。于高明之见。以为如何。明德章句宾主之说。所见略同。不必更烦。而未发中气质本色自在之说。书谕面诲虽缕缕。浅陋之识。卒未骤悟。此恐先入为主而然也。请更奉质焉。窃谓未发。如止水明镜。言其气则未用事而虚灵不昧。言其理则无偏倚而浑然纯善。当此时节。固无气禀之陋。而至若气质之病。则方于已发处可见。今若谓未发之前。有善无恶。则是湛一之体。复其本然而已。不可又谓美恶自在。若曰未发之时。美恶自在。则是病根在里。伏而未作。不可又谓纯善无恶。两说似难并行矣。何以明之。谨按朱子曰寂然不动者诚也注。本然而未发者。实理之体。又曰诚精故明注。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小注。朱子曰。诚精者。直是无些夹杂。如一块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7H 页
 银。更无铜铅。便是通透好银。(通书圣第四章。)尤庵曰。所谓未发。必肃然不乱。莹然不昏。虽鬼神有不得窥其际者。然后方可得以名之。栗谷曰。气质固有美恶之一定者。非但其性之本然。而昏昧杂扰。故不可谓未发也。未发者。性之本然也。昏昧杂扰。则气已掩性。故不可谓性之体也。以此诸说观之。方其未发。气清理明。复其本善。可见好银无铜铅之杂。而况气质昏乱之病。果与未发时肃然莹然体段。有若阴阳昼夜之不相入。其可谓夹杂隐伏于未发之中耶。又按昔者或问直出者为善。旁出者为恶。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横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无源。于此可见未发之时。有善有恶。而程子所谓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者。盖谓此也。若谓善恶。东西相对。彼此角立。则未发之前。已具此两端。而所谓天命之性。亦甚纡杂矣。朱子曰得之。以此观之。未发之前。清浊美恶。若果自在。则是恶非横生而乃固有也。恶非无源而乃有本也。美恶两端。未免相对并立。元无先后。而大本有纡杂之病矣。其可谓纯善无恶乎。此所以李横城所谓清浊美恶自在之说及有善无恶之说。不得不前后矛盾。而李丈则以为虽有浊本色。不可谓有恶种子。高明则以
银。更无铜铅。便是通透好银。(通书圣第四章。)尤庵曰。所谓未发。必肃然不乱。莹然不昏。虽鬼神有不得窥其际者。然后方可得以名之。栗谷曰。气质固有美恶之一定者。非但其性之本然。而昏昧杂扰。故不可谓未发也。未发者。性之本然也。昏昧杂扰。则气已掩性。故不可谓性之体也。以此诸说观之。方其未发。气清理明。复其本善。可见好银无铜铅之杂。而况气质昏乱之病。果与未发时肃然莹然体段。有若阴阳昼夜之不相入。其可谓夹杂隐伏于未发之中耶。又按昔者或问直出者为善。旁出者为恶。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横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无源。于此可见未发之时。有善有恶。而程子所谓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者。盖谓此也。若谓善恶。东西相对。彼此角立。则未发之前。已具此两端。而所谓天命之性。亦甚纡杂矣。朱子曰得之。以此观之。未发之前。清浊美恶。若果自在。则是恶非横生而乃固有也。恶非无源而乃有本也。美恶两端。未免相对并立。元无先后。而大本有纡杂之病矣。其可谓纯善无恶乎。此所以李横城所谓清浊美恶自在之说及有善无恶之说。不得不前后矛盾。而李丈则以为虽有浊本色。不可谓有恶种子。高明则以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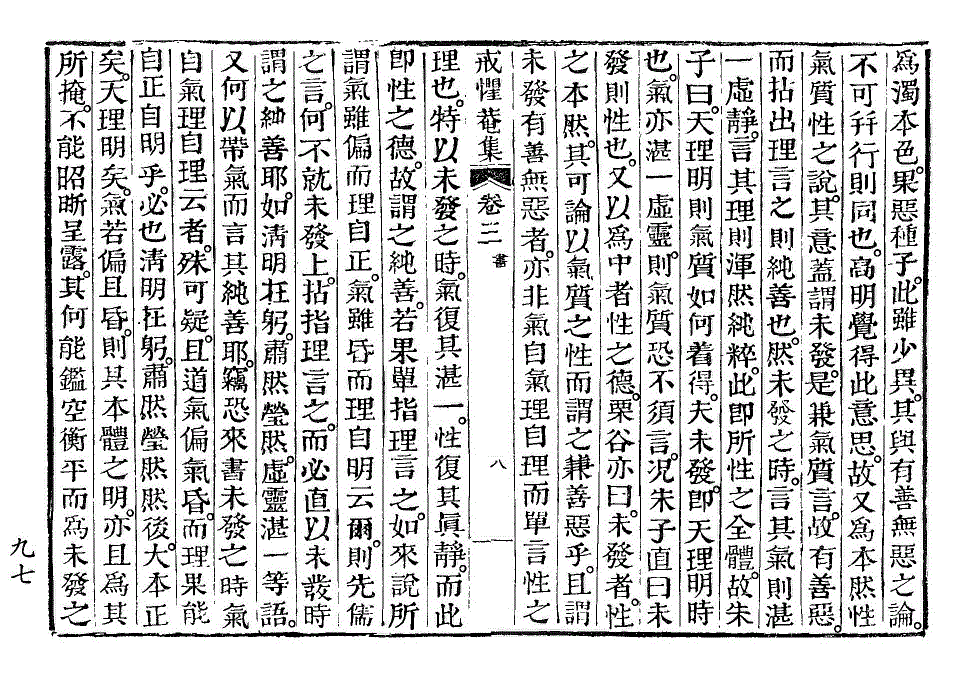 为浊本色。果恶种子。此虽少异。其与有善无恶之论。不可并行则同也。高明觉得此意思。故又为本然性气质性之说。其意盖谓未发。是兼气质言。故有善恶。而拈出理言之则纯善也。然未发之时。言其气则湛一虚静。言其理则浑然纯粹。此即所性之全体。故朱子曰。天理明则气质如何着得。夫未发。即天理明时也。气亦湛一虚灵。则气质恐不须言。况朱子直曰未发则性也。又以为中者性之德。栗谷亦曰。未发者。性之本然。其可论以气质之性而谓之兼善恶乎。且谓未发有善无恶者。亦非气自气理自理而单言性之理也。特以未发之时。气复其湛一。性复其真静。而此即性之德。故谓之纯善。若果单指理言之。如来说所谓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昏而理自明云尔。则先儒之言。何不就未发上。拈指理言之。而必直以未发时谓之纯善耶。如清明在躬。肃然莹然。虚灵湛一等语。又何以带气而言其纯善耶。窃恐来书未发之时气自气理自理云者。殊可疑。且道气偏气昏。而理果能自正自明乎。必也清明在躬。肃然莹然然后。大本正矣。天理明矣。气若偏且昏。则其本体之明。亦且为其所掩。不能昭晢呈露。其何能鉴空衡平而为未发之
为浊本色。果恶种子。此虽少异。其与有善无恶之论。不可并行则同也。高明觉得此意思。故又为本然性气质性之说。其意盖谓未发。是兼气质言。故有善恶。而拈出理言之则纯善也。然未发之时。言其气则湛一虚静。言其理则浑然纯粹。此即所性之全体。故朱子曰。天理明则气质如何着得。夫未发。即天理明时也。气亦湛一虚灵。则气质恐不须言。况朱子直曰未发则性也。又以为中者性之德。栗谷亦曰。未发者。性之本然。其可论以气质之性而谓之兼善恶乎。且谓未发有善无恶者。亦非气自气理自理而单言性之理也。特以未发之时。气复其湛一。性复其真静。而此即性之德。故谓之纯善。若果单指理言之。如来说所谓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昏而理自明云尔。则先儒之言。何不就未发上。拈指理言之。而必直以未发时谓之纯善耶。如清明在躬。肃然莹然。虚灵湛一等语。又何以带气而言其纯善耶。窃恐来书未发之时气自气理自理云者。殊可疑。且道气偏气昏。而理果能自正自明乎。必也清明在躬。肃然莹然然后。大本正矣。天理明矣。气若偏且昏。则其本体之明。亦且为其所掩。不能昭晢呈露。其何能鉴空衡平而为未发之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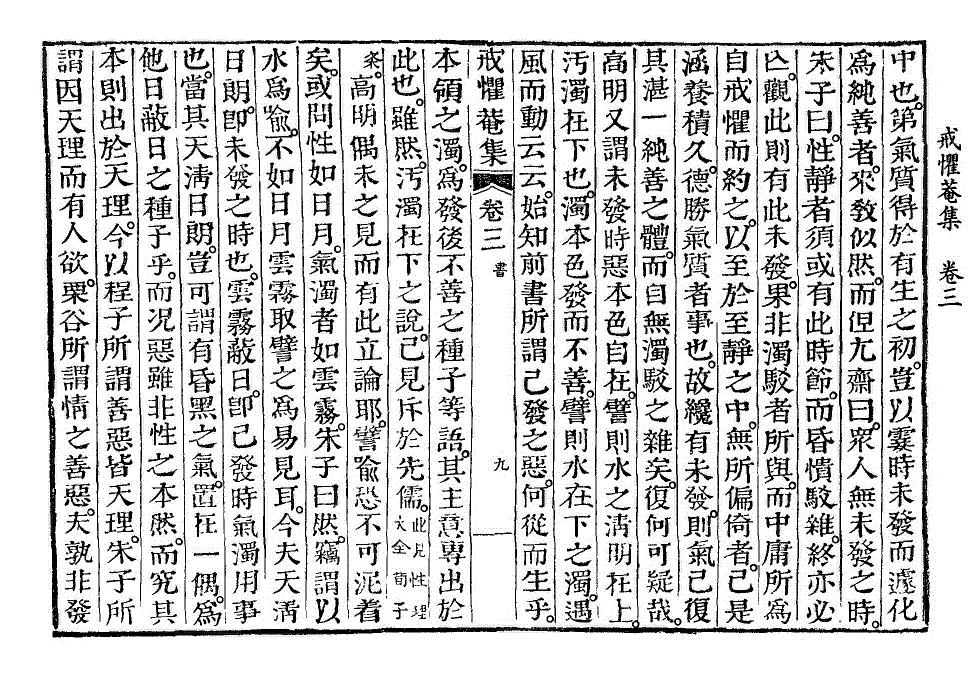 中也。第气质得于有生之初。岂以霎时未发而遽化为纯善者。来教似然。而但尤斋曰。众人无未发之时。朱子曰。性静者须或有此时节。而昏愦驳杂。终亦必亡。观此则有此未发。果非浊驳者所与。而中庸所为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者。已是涵养积久。德胜气质者事也。故才有未发。则气已复其湛一纯善之体。而自无浊驳之杂矣。复何可疑哉。高明又谓未发时恶本色自在。譬则水之清明在上。污浊在下也。浊本色发而不善。譬则水在下之浊。遇风而动云云。始知前书所谓已发之恶。何从而生乎。本领之浊。为发后不善之种子等语。其主意专出于此也。虽然。污浊在下之说。已见斥于先儒。(此见性理大全荀子条。)高明偶未之见而有此立论耶。譬喻恐不可泥着矣。或问性如日月。气浊者如云雾。朱子曰然。窃谓以水为喻。不如日月云雾取譬之为易见耳。今夫天清日朗。即未发之时也。云雾蔽日。即已发时气浊用事也。当其天清日朗。岂可谓有昏黑之气。置在一偶。为他日蔽日之种子乎。而况恶虽非性之本然。而究其本则出于天理。今以程子所谓善恶皆天理。朱子所谓因天理而有人欲。栗谷所谓情之善恶。夫孰非发
中也。第气质得于有生之初。岂以霎时未发而遽化为纯善者。来教似然。而但尤斋曰。众人无未发之时。朱子曰。性静者须或有此时节。而昏愦驳杂。终亦必亡。观此则有此未发。果非浊驳者所与。而中庸所为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者。已是涵养积久。德胜气质者事也。故才有未发。则气已复其湛一纯善之体。而自无浊驳之杂矣。复何可疑哉。高明又谓未发时恶本色自在。譬则水之清明在上。污浊在下也。浊本色发而不善。譬则水在下之浊。遇风而动云云。始知前书所谓已发之恶。何从而生乎。本领之浊。为发后不善之种子等语。其主意专出于此也。虽然。污浊在下之说。已见斥于先儒。(此见性理大全荀子条。)高明偶未之见而有此立论耶。譬喻恐不可泥着矣。或问性如日月。气浊者如云雾。朱子曰然。窃谓以水为喻。不如日月云雾取譬之为易见耳。今夫天清日朗。即未发之时也。云雾蔽日。即已发时气浊用事也。当其天清日朗。岂可谓有昏黑之气。置在一偶。为他日蔽日之种子乎。而况恶虽非性之本然。而究其本则出于天理。今以程子所谓善恶皆天理。朱子所谓因天理而有人欲。栗谷所谓情之善恶。夫孰非发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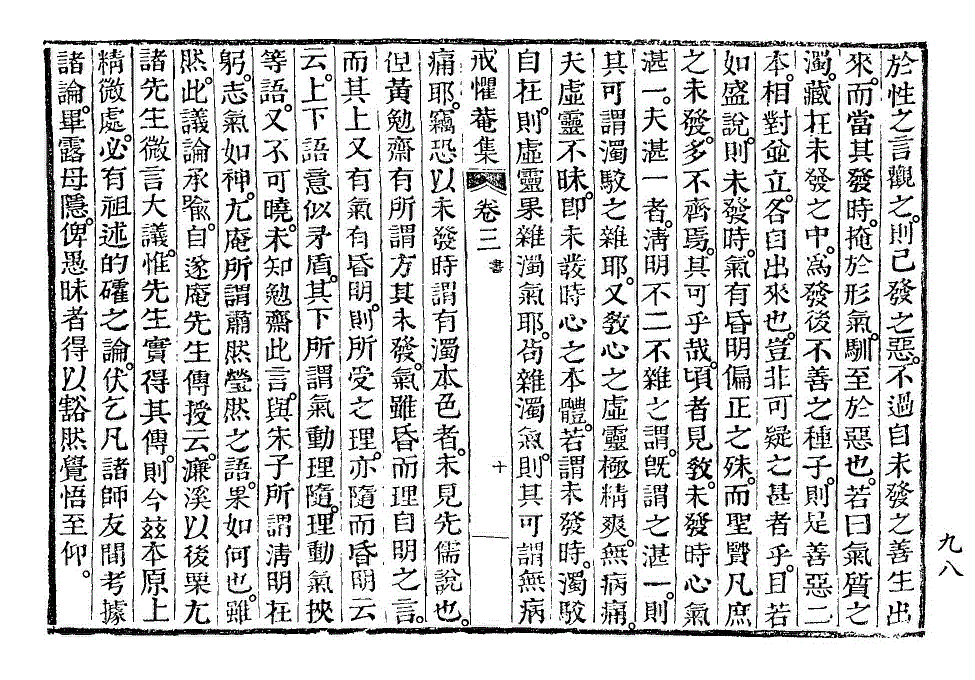 于性之言观之。则已发之恶。不过自未发之善生出来。而当其发时。掩于形气。驯至于恶也。若曰气质之浊。藏在未发之中。为发后不善之种子。则是善恶二本。相对并立。各自出来也。岂非可疑之甚者乎。且若如盛说。则未发时。气有昏明偏正之殊。而圣贤凡庶之未发。多不齐焉。其可乎哉。顷者见教。未发时心气湛一。夫湛一者。清明不二不杂之谓。既谓之湛一。则其可谓浊驳之杂耶。又教心之虚灵极精爽。无病痛。夫虚灵不昧。即未发时心之本体。若谓未发时。浊驳自在。则虚灵果杂浊气耶。苟杂浊气。则其可谓无病痛耶。窃恐以未发时谓有浊本色者。未见先儒说也。但黄勉斋有所谓方其未发。气虽昏而理自明之言。而其上又有气有昏明。则所受之理。亦随而昏明云云。上下语意似矛盾。其下所谓气动理随。理动气挟等语。又不可晓。未知勉斋此言。与朱子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尤庵所谓肃然莹然之语。果如何也。虽然。此议论承喻。自遂庵先生传授云。濂溪以后栗尤诸先生微言大议。惟先生实得其传。则今玆本原上精微处。必有祖述的礭之论。伏乞凡诸师友间考据诸论。毕露毋隐。俾愚昧者得以豁然觉悟至仰。
于性之言观之。则已发之恶。不过自未发之善生出来。而当其发时。掩于形气。驯至于恶也。若曰气质之浊。藏在未发之中。为发后不善之种子。则是善恶二本。相对并立。各自出来也。岂非可疑之甚者乎。且若如盛说。则未发时。气有昏明偏正之殊。而圣贤凡庶之未发。多不齐焉。其可乎哉。顷者见教。未发时心气湛一。夫湛一者。清明不二不杂之谓。既谓之湛一。则其可谓浊驳之杂耶。又教心之虚灵极精爽。无病痛。夫虚灵不昧。即未发时心之本体。若谓未发时。浊驳自在。则虚灵果杂浊气耶。苟杂浊气。则其可谓无病痛耶。窃恐以未发时谓有浊本色者。未见先儒说也。但黄勉斋有所谓方其未发。气虽昏而理自明之言。而其上又有气有昏明。则所受之理。亦随而昏明云云。上下语意似矛盾。其下所谓气动理随。理动气挟等语。又不可晓。未知勉斋此言。与朱子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尤庵所谓肃然莹然之语。果如何也。虽然。此议论承喻。自遂庵先生传授云。濂溪以后栗尤诸先生微言大议。惟先生实得其传。则今玆本原上精微处。必有祖述的礭之论。伏乞凡诸师友间考据诸论。毕露毋隐。俾愚昧者得以豁然觉悟至仰。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9H 页
 顷承面诲。又以大学正心全属未发工夫。愚则以为当兼未发已发言。忿懥等既是已发后病。则治此忿懥等工夫。岂可全谓未发工夫耶。盛教又以为正心只是除去浮念而已。修身章。方言应物偏重之病者。亦似可疑。事未来事已过时。固可谓浮念。而正应事时。偏系亦岂非应物偏重之病耶。修身章五个辟字。固皆心之病。而朱子曰。忿懥等。是心与物接时事。亲爱等。是身与物接时事。又曰。修身以后。大槩说向接物待人去。又与只说心处不同。夫既说偏系之病于正心。又说偏僻之病于修身者。固何所妨。而必以偏病归之修身耶。高明以圣学辑要所谓戒惧者静存而正心之属也。谨独者动察而诚意之属也云云为證。而此亦有曲折。盖正心是兼未发言。故栗谷以庸学首章表里分配。而戒惧则属之正心。慎独则属之诚意也。若果以正心全属于未发工夫。则修己篇(辑要)正心章。何以统属涵养省察。而又以大学有所忿懥以下。属之省察条耶。此等分配处。恐当活看矣。窃谓胡云峰所谓此章正自有存养省察工夫者。可谓礭论矣。未知高明以为如何。
顷承面诲。又以大学正心全属未发工夫。愚则以为当兼未发已发言。忿懥等既是已发后病。则治此忿懥等工夫。岂可全谓未发工夫耶。盛教又以为正心只是除去浮念而已。修身章。方言应物偏重之病者。亦似可疑。事未来事已过时。固可谓浮念。而正应事时。偏系亦岂非应物偏重之病耶。修身章五个辟字。固皆心之病。而朱子曰。忿懥等。是心与物接时事。亲爱等。是身与物接时事。又曰。修身以后。大槩说向接物待人去。又与只说心处不同。夫既说偏系之病于正心。又说偏僻之病于修身者。固何所妨。而必以偏病归之修身耶。高明以圣学辑要所谓戒惧者静存而正心之属也。谨独者动察而诚意之属也云云为證。而此亦有曲折。盖正心是兼未发言。故栗谷以庸学首章表里分配。而戒惧则属之正心。慎独则属之诚意也。若果以正心全属于未发工夫。则修己篇(辑要)正心章。何以统属涵养省察。而又以大学有所忿懥以下。属之省察条耶。此等分配处。恐当活看矣。窃谓胡云峰所谓此章正自有存养省察工夫者。可谓礭论矣。未知高明以为如何。答沈信夫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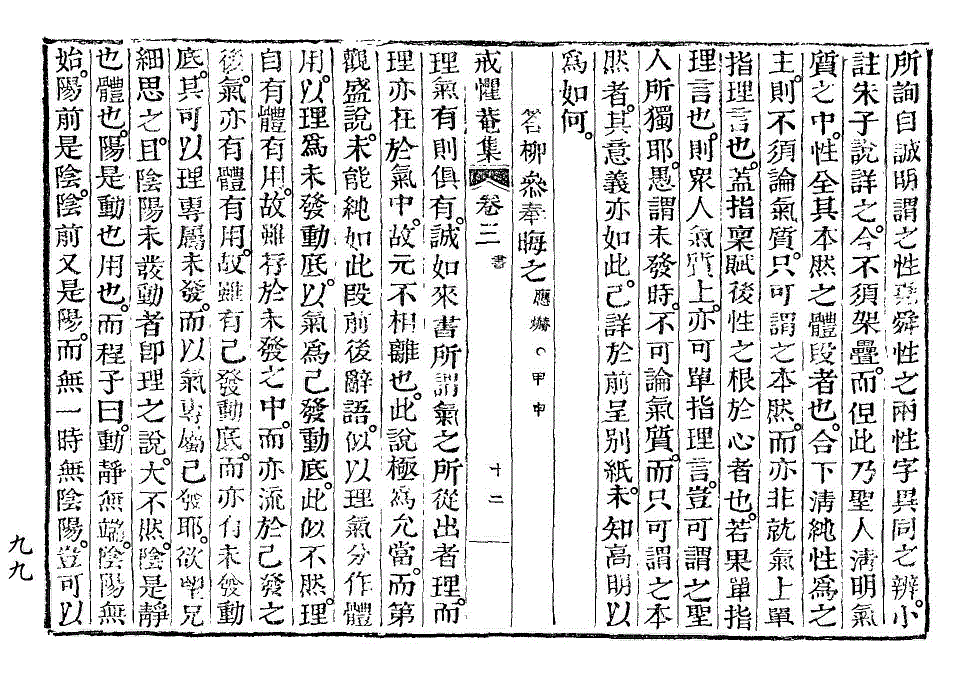 所询自诚明谓之性尧舜性之两性字异同之辨。小注朱子说详之。今不须架叠。而但此乃圣人清明气质之中。性全其本然之体段者也。合下清纯性为之主。则不须论气质。只可谓之本然。而亦非就气上单指理言也。盖指禀赋后性之根于心者也。若果单指理言也。则众人气质上。亦可单指理言。岂可谓之圣人所独耶。愚谓未发时。不可论气质。而只可谓之本然者。其意义亦如此。已详于前呈别纸。未知高明以为如何。
所询自诚明谓之性尧舜性之两性字异同之辨。小注朱子说详之。今不须架叠。而但此乃圣人清明气质之中。性全其本然之体段者也。合下清纯性为之主。则不须论气质。只可谓之本然。而亦非就气上单指理言也。盖指禀赋后性之根于心者也。若果单指理言也。则众人气质上。亦可单指理言。岂可谓之圣人所独耶。愚谓未发时。不可论气质。而只可谓之本然者。其意义亦如此。已详于前呈别纸。未知高明以为如何。答柳参奉晦之(应赫○甲申)
理气有则俱有。诚如来书所谓气之所从出者理。而理亦在于气中。故元不相离也。此说极为允当。而第观盛说。未能纯如此段前后辞语。似以理气分作体用。以理为未发动底。以气为已发动底。此似不然。理自有体有用。故虽存于未发之中。而亦流于已发之后。气亦有体有用。故虽有已发动底。而亦有未发动底。其可以理专属未发。而以气专属已发耶。欲望兄细思之。且阴阳未发动者即理之说。大不然。阴是静也体也。阳是动也用也。而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阳前是阴。阴前又是阳。而无一时无阴阳。岂可以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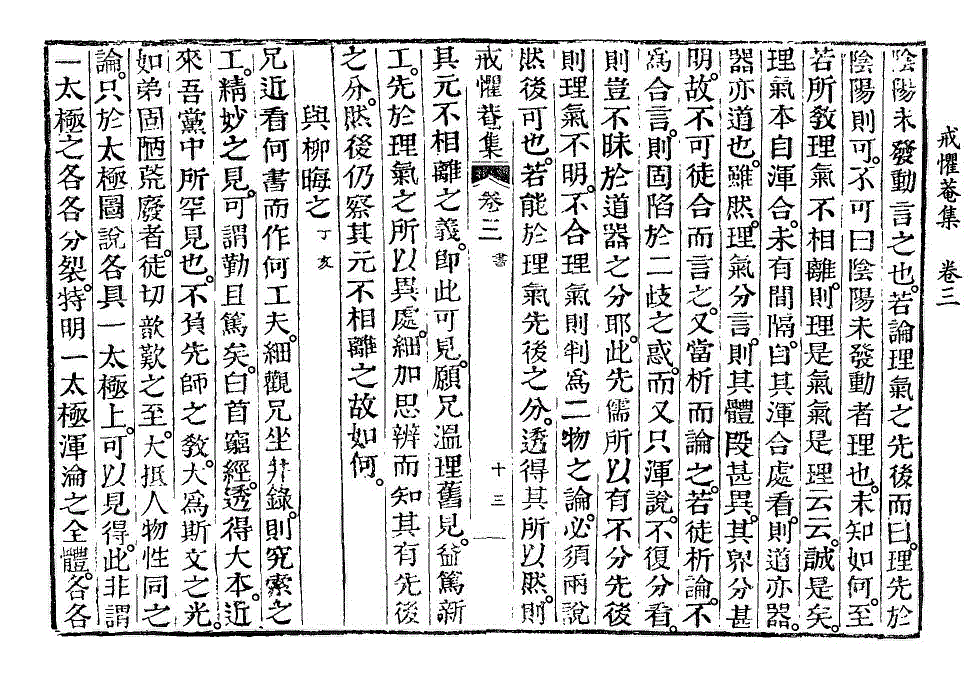 阴阳未发动言之也。若论理气之先后而曰。理先于阴阳则可。不可曰阴阳未发动者理也。未知如何。至若所教理气不相离。则理是气气是理云云。诚是矣。理气本自浑合。未有间隔。自其浑合处看。则道亦器。器亦道也。虽然。理气分言。则其体段甚异。其界分甚明。故不可徒合而言之。又当析而论之。若徒析论。不为合言。则固陷于二歧之惑。而又只浑说。不复分看。则岂不昧于道器之分耶。此先儒所以有不分先后则理气不明。不合理气则判为二物之论。必须两说然后可也。若能于理气先后之分。透得其所以然。则其元不相离之义。即此可见。愿兄温理旧见。益笃新工。先于理气之所以异处。细加思辨而知其有先后之分。然后仍察其元不相离之故如何。
阴阳未发动言之也。若论理气之先后而曰。理先于阴阳则可。不可曰阴阳未发动者理也。未知如何。至若所教理气不相离。则理是气气是理云云。诚是矣。理气本自浑合。未有间隔。自其浑合处看。则道亦器。器亦道也。虽然。理气分言。则其体段甚异。其界分甚明。故不可徒合而言之。又当析而论之。若徒析论。不为合言。则固陷于二歧之惑。而又只浑说。不复分看。则岂不昧于道器之分耶。此先儒所以有不分先后则理气不明。不合理气则判为二物之论。必须两说然后可也。若能于理气先后之分。透得其所以然。则其元不相离之义。即此可见。愿兄温理旧见。益笃新工。先于理气之所以异处。细加思辨而知其有先后之分。然后仍察其元不相离之故如何。与柳晦之(丁亥)
兄近看何书而作何工夫。细观兄坐井录。则究索之工。精妙之见。可谓勤且笃矣。白首穷经。透得大本。近来吾党中所罕见也。不负先师之教。大为斯文之光。如弟固陋荒废者。徒切歆叹之至。大抵人物性同之论。只于太极图说各具一太极上。可以见得。此非谓一太极之各各分裂。特明一太极浑沦之全体。各各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0L 页
 全具于万物中。来示所谓既言太极于生阴生阳。而复言无极之真于生万物者。其明太极本体不分之理者。极为明矣。且所谓理无往而不全。气无往而不分。气虽不同而性无不同者。果然矣。但盛论宗旨。又以人物始生于天一之数。故理不分而为一。是虽自得之见。而刱见者。极涉生新。未知此有依据考證耶。今只曰理纯善而无杂。故无往不全。气有清浊而不齐。故禀有不同云则好矣。何必言以一数之禀而理不分也。望更思而教之如何。吾儒之论。只当就圣贤之所已言。究索而遵承而已。不必刱意立说。以求新奇之妙也。朱子曰。读书。且就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玩味之。自见意味可也。欲于传注之外。别求自得而务立新说。则用心愈劳而去道愈远。又曰。自得者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说而必自己出耳。朱夫子此说。政合受用。未知兄以为如何。兄既欲往复。缕缕言之。且吾同志之间。书言无讳。政所谓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于渠者。故敢就录中。随其疑处。逐条仰质。更望垂览后回赐可否。以破蒙见如何。
全具于万物中。来示所谓既言太极于生阴生阳。而复言无极之真于生万物者。其明太极本体不分之理者。极为明矣。且所谓理无往而不全。气无往而不分。气虽不同而性无不同者。果然矣。但盛论宗旨。又以人物始生于天一之数。故理不分而为一。是虽自得之见。而刱见者。极涉生新。未知此有依据考證耶。今只曰理纯善而无杂。故无往不全。气有清浊而不齐。故禀有不同云则好矣。何必言以一数之禀而理不分也。望更思而教之如何。吾儒之论。只当就圣贤之所已言。究索而遵承而已。不必刱意立说。以求新奇之妙也。朱子曰。读书。且就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玩味之。自见意味可也。欲于传注之外。别求自得而务立新说。则用心愈劳而去道愈远。又曰。自得者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说而必自己出耳。朱夫子此说。政合受用。未知兄以为如何。兄既欲往复。缕缕言之。且吾同志之间。书言无讳。政所谓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于渠者。故敢就录中。随其疑处。逐条仰质。更望垂览后回赐可否。以破蒙见如何。别纸(坐井录条卞)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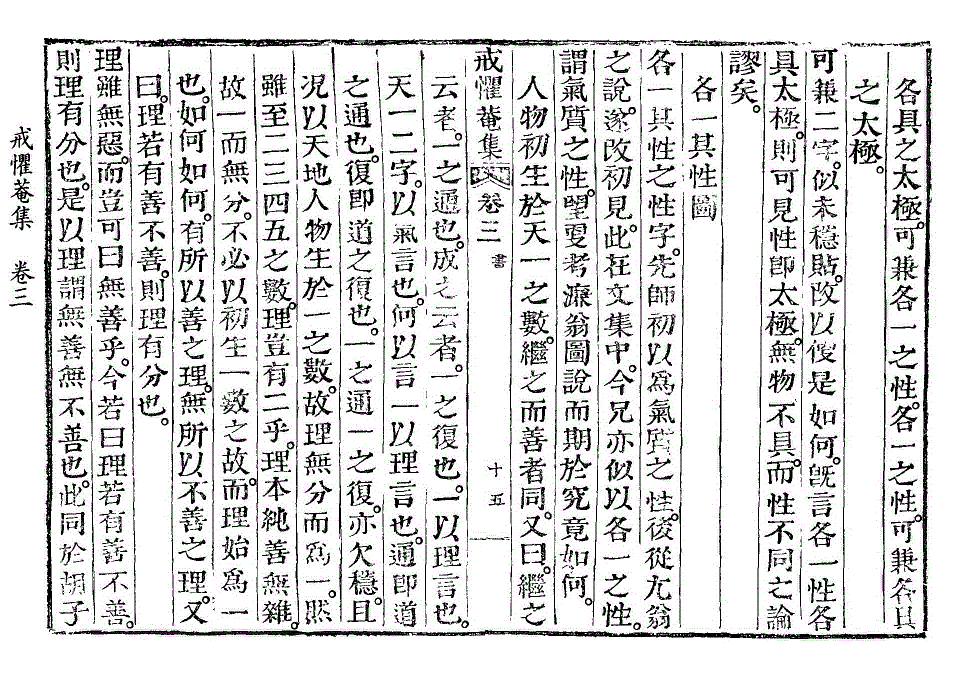 各具之太极。可兼各一之性。各一之性。可兼各具之太极。
各具之太极。可兼各一之性。各一之性。可兼各具之太极。可兼二字。似未稳贴。改以便是如何。既言各一性各具太极。则可见性即太极。无物不具。而性不同之论谬矣。
各一其性图
各一其性之性字。先师初以为气质之性。后从尤翁之说。遂改初见。此在文集中。今兄亦似以各一之性。谓气质之性。望更考濂翁图说而期于究竟如何。
人物初生于天一之数。继之而善者同。又曰。继之云者。一之通也。成之云者。一之复也。一以理言也。天一二字。以气言也。何以言一以理言也。通即道之通也。复即道之复也。一之通一之复。亦欠稳。且况以天地人物生于一之数。故理无分而为一。然虽至二三四五之数。理岂有二乎。理本纯善无杂。故一而无分。不必以初生一数之故。而理始为一也。如何如何。有所以善之理。无所以不善之理。又曰。理若有善不善。则理有分也。
理虽无恶。而岂可曰无善乎。今若曰理若有善不善。则理有分也。是以理谓无善无不善也。此同于胡子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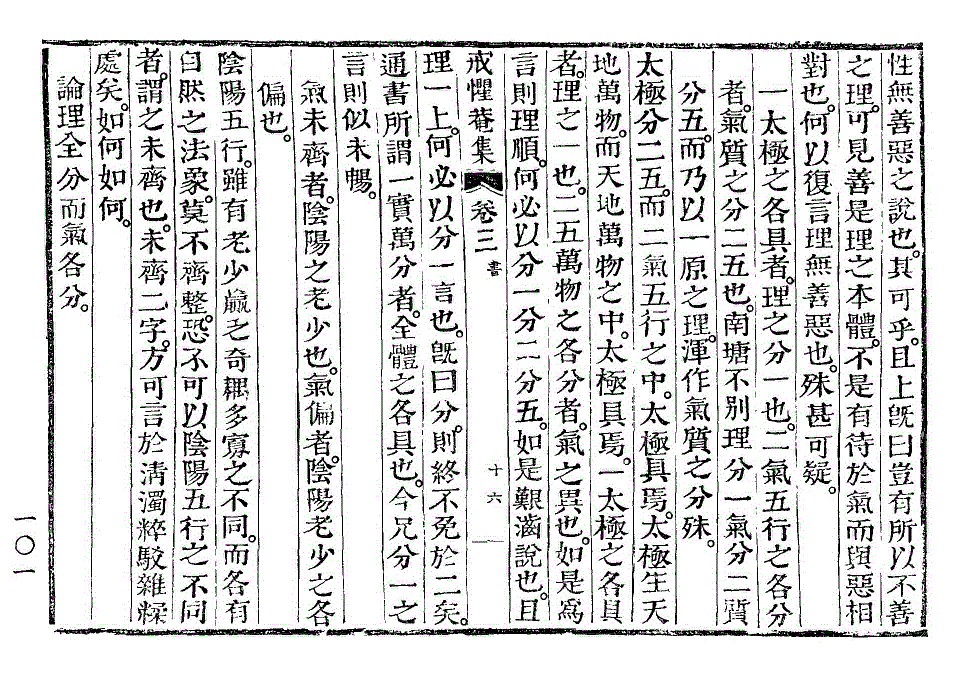 性无善恶之说也。其可乎。且上既曰岂有所以不善之理。可见善是理之本体。不是有待于气而与恶相对也。何以复言理无善恶也。殊甚可疑。
性无善恶之说也。其可乎。且上既曰岂有所以不善之理。可见善是理之本体。不是有待于气而与恶相对也。何以复言理无善恶也。殊甚可疑。一太极之各具者。理之分一也。二气五行之各分者。气质之分二五也。南塘不别理分一气分二质分五。而乃以一原之理。浑作气质之分殊。
太极分二五。而二气五行之中。太极具焉。太极生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之中。太极具焉。一太极之各具者。理之一也。二五万物之各分者。气之异也。如是为言则理顺。何必以分一分二分五。如是艰𤁧说也。且理一上。何必以分一言也。既曰分。则终不免于二矣。通书所谓一实万分者。全体之各具也。今兄分一之言则似未畅。
气未齐者。阴阳之老少也。气偏者。阴阳老少之各偏也。
阴阳五行。虽有老少赢乏奇耦多寡之不同。而各有自然之法象。莫不齐整。恐不可以阴阳五行之不同者。谓之未齐也。未齐二字。方可言于清浊粹驳杂糅处矣。如何如何。
论理全分而气各分。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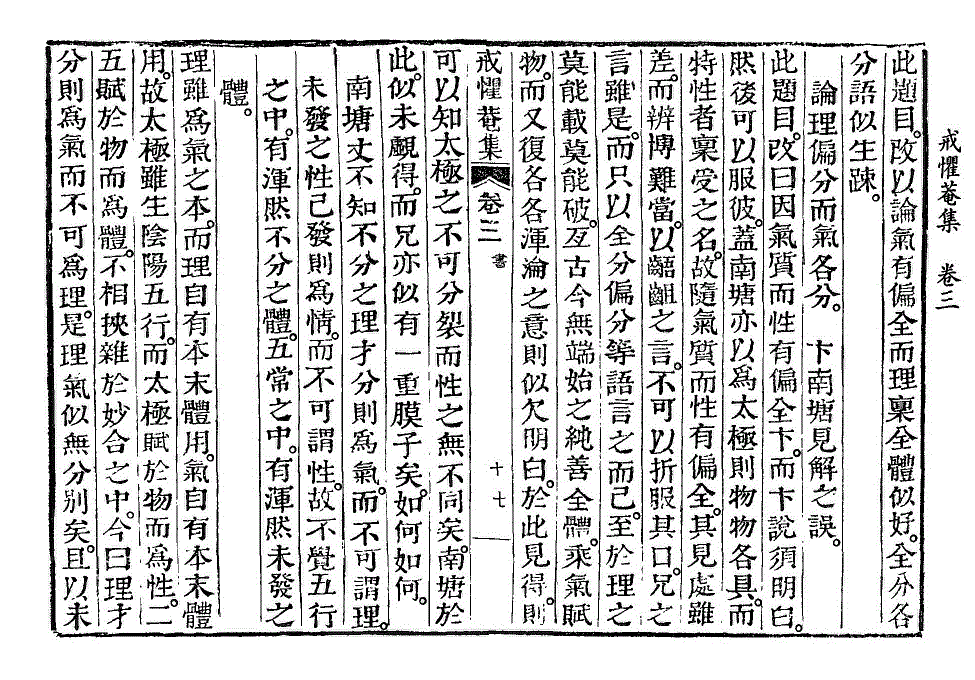 此题目。改以论气有偏全而理禀全体似好。全分各分语似生疏。
此题目。改以论气有偏全而理禀全体似好。全分各分语似生疏。论理偏分而气各分。 卞南塘见解之误。
此题目。改曰因气质而性有偏全卞。而卞说须明白。然后可以服彼。盖南塘亦以为太极则物物各具。而特性者禀受之名。故随气质而性有偏全。其见处虽差。而辨博难当。以龉龃之言。不可以折服其口。兄之言虽是。而只以全分偏分等语言之而已。至于理之莫能载莫能破。亘古今无端始之纯善全体。乘气赋物。而又复各各浑沦之意则似欠明白。于此见得。则可以知太极之不可分裂而性之无不同矣。南塘于此。似未觑得。而兄亦似有一重膜子矣。如何如何。
南塘丈不知不分之理才分则为气。而不可谓理。未发之性已发则为情。而不可谓性。故不觉五行之中。有浑然不分之体。五常之中。有浑然未发之体。
理虽为气之本。而理自有本末体用。气自有本末体用。故太极虽生阴阳五行。而太极赋于物而为性。二五赋于物而为体。不相挟杂于妙合之中。今曰理才分则为气而不可为理。是理气似无分别矣。且以未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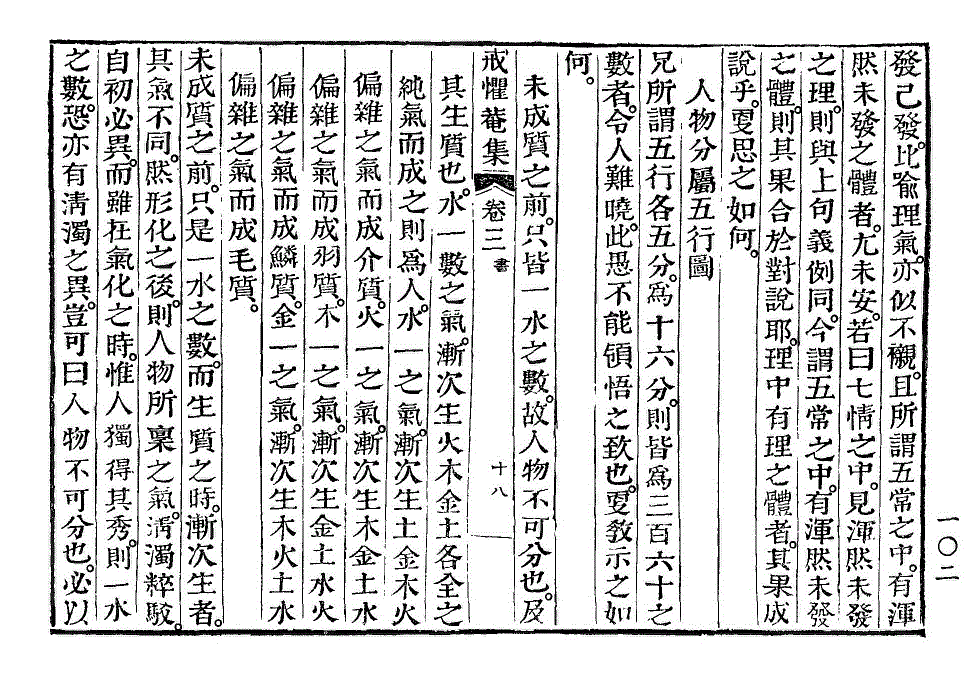 发已发。比喻理气。亦似不衬。且所谓五常之中。有浑然未发之体者。尤未安。若曰七情之中。见浑然未发之理。则与上句义例同。今谓五常之中。有浑然未发之体。则其果合于对说耶。理中有理之体者。其果成说乎。更思之如何。
发已发。比喻理气。亦似不衬。且所谓五常之中。有浑然未发之体者。尤未安。若曰七情之中。见浑然未发之理。则与上句义例同。今谓五常之中。有浑然未发之体。则其果合于对说耶。理中有理之体者。其果成说乎。更思之如何。人物分属五行图
兄所谓五行各五分。为十六分。则皆为三百六十之数者。令人难晓。此愚不能领悟之致也。更教示之如何。
未成质之前。只皆一水之数。故人物不可分也。及其生质也。水一数之气。渐次生火木金土各全之纯气而成之则为人。水一之气。渐次生土金木火偏杂之气而成介质。火一之气。渐次生木金土水偏杂之气而成羽质。木一之气。渐次生金土水火偏杂之气而成鳞质。金一之气。渐次生木火土水偏杂之气而成毛质。
未成质之前。只是一水之数。而生质之时。渐次生者。其气不同。然形化之后。则人物所禀之气。清浊粹驳。自初必异。而虽在气化之时。惟人独得其秀。则一水之数。恐亦有清浊之异。岂可曰人物不可分也。必以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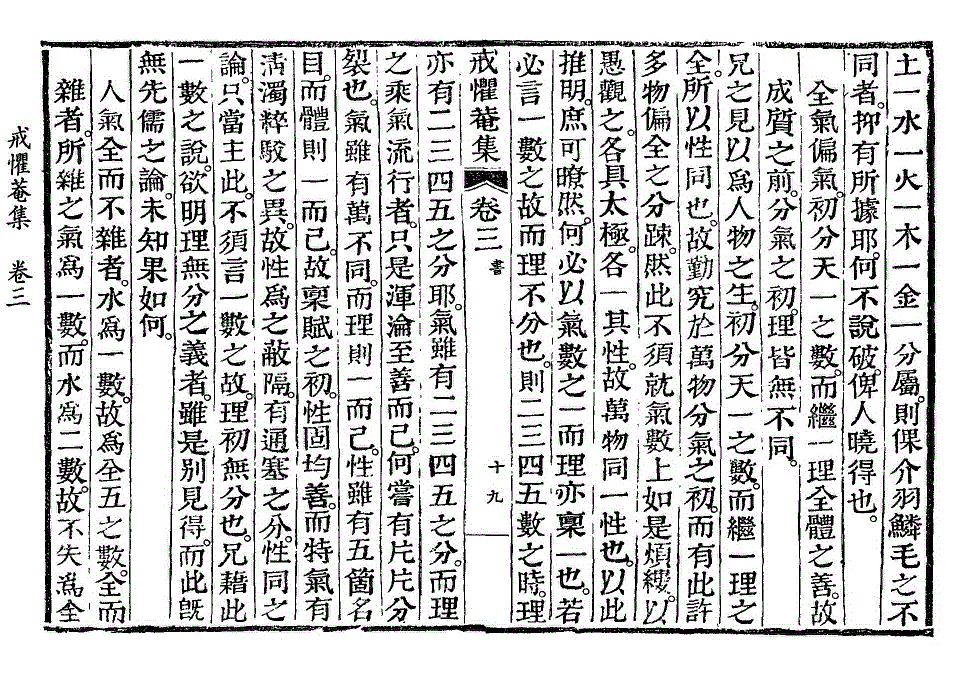 土一水一火一木一金一分属。则裸介羽鳞毛之不同者。抑有所据耶。何不说破。俾人晓得也。
土一水一火一木一金一分属。则裸介羽鳞毛之不同者。抑有所据耶。何不说破。俾人晓得也。全气偏气。初分天一之数。而继一理全体之善。故成质之前。分气之初。理皆无不同。
兄之见以为人物之生。初分天一之数。而继一理之全。所以性同也。故勤究于万物分气之初。而有此许多物偏全之分疏。然此不须就气数上如是烦缕。以愚观之。各具太极。各一其性。故万物同一性也。以此推明。庶可暸然。何必以气数之一而理亦禀一也。若必言一数之故而理不分也。则二三四五数之时。理亦有二三四五之分耶。气虽有二三四五之分。而理之乘气流行者。只是浑沦至善而已。何尝有片片分裂也。气虽有万不同。而理则一而已。性虽有五个名目。而体则一而已。故禀赋之初。性固均善。而特气有清浊粹驳之异。故性为之蔽隔。有通塞之分。性同之论。只当主此。不须言一数之故。理初无分也。兄藉此一数之说。欲明理无分之义者。虽是别见得。而此既无先儒之论。未知果如何。
人气全而不杂者。水为一数。故为全五之数。全而杂者。所杂之气为一数。而水为二数。故不失为全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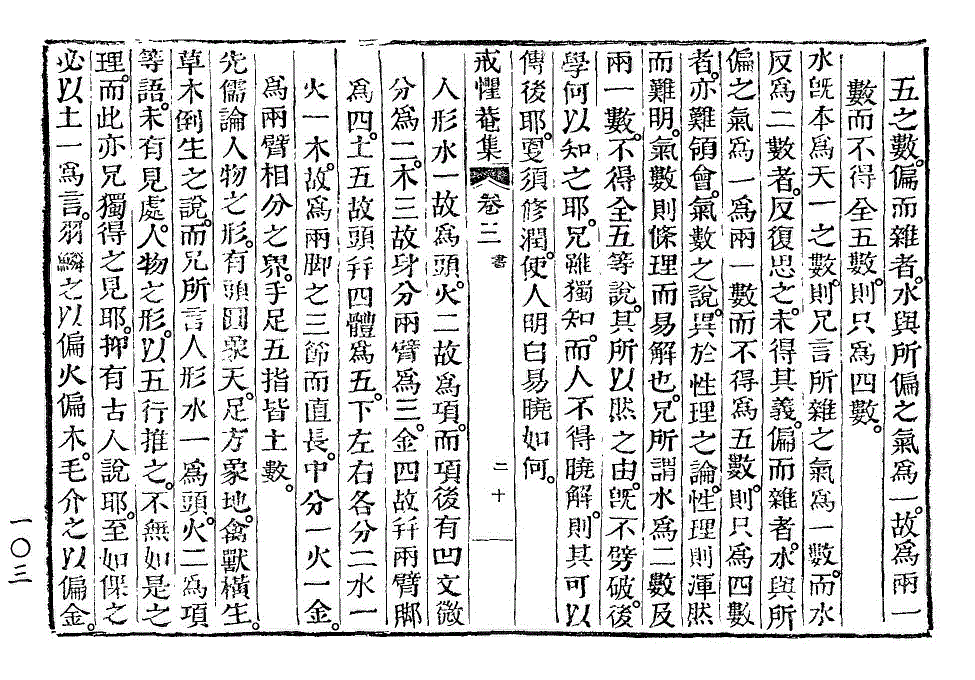 五之数。偏而杂者。水与所偏之气为一。故为两一数而不得全五数。则只为四数。
五之数。偏而杂者。水与所偏之气为一。故为两一数而不得全五数。则只为四数。水既本为天一之数。则兄言所杂之气为一数。而水反为二数者。反复思之。未得其义。偏而杂者。水与所偏之气为一为两一数而不得为五数。则只为四数者。亦难领会。气数之说。异于性理之论。性理则浑然而难明。气数则条理而易解也。兄所谓水为二数及两一数。不得全五等说。其所以然之由。既不劈破。后学何以知之耶。兄虽独知。而人不得晓解。则其可以传后耶。更须修润。使人明白易晓如何。
人形水一故为头。火二故为项。而项后有凹文微分为二。木三故身分两臂为三。金四故并两臂脚为四。土五故头并四体为五。下左右各分二水一火一木。故为两脚之三节而直长。中分一火一金。为两臂相分之界。手足五指皆土数。
先儒论人物之形。有头圆象天。足方象地。禽兽横生。草木倒生之说。而兄所言人形水一为头。火二为项等语。未有见处。人物之形。以五行推之。不无如是之理。而此亦兄独得之见耶。抑有古人说耶。至如裸之必以土一为言。羽鳞之以偏火偏木。毛介之以偏金。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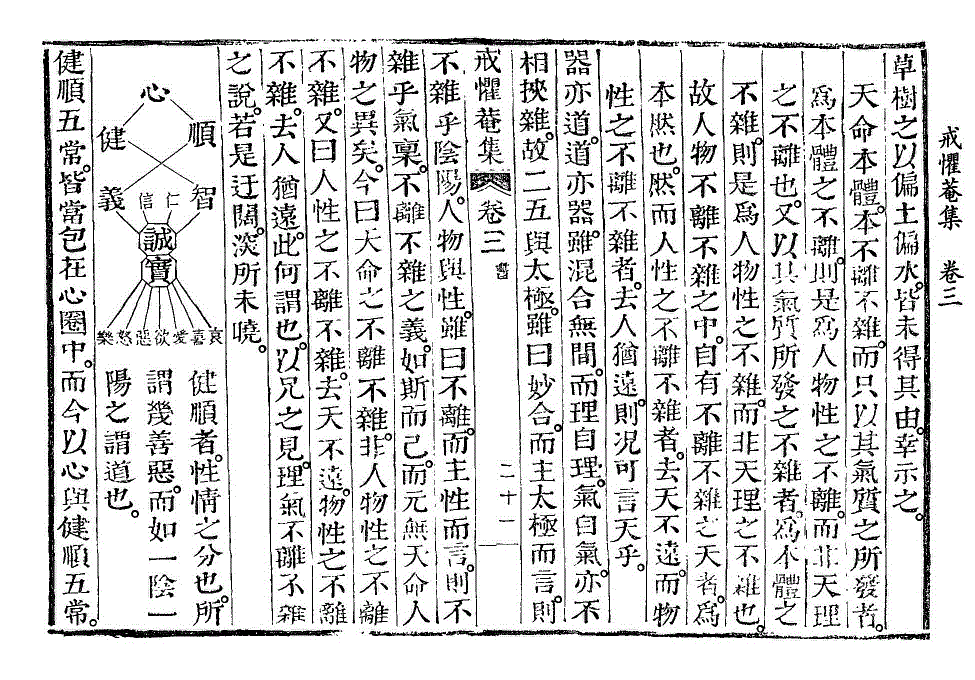 草树之以偏土偏水。皆未得其由。幸示之。
草树之以偏土偏水。皆未得其由。幸示之。天命本体。本不离不杂。而只以其气质之所发者。为本体之不离。则是为人物性之不离。而非天理之不离也。又以其气质所发之不杂者。为本体之不杂。则是为人物性之不杂。而非天理之不杂也。故人物不离不杂之中。自有不离不杂之天者。为本然也。然而人性之不离不杂者。去天不远。而物性之不离不杂者。去人犹远。则况可言天乎。
器亦道。道亦器。虽混合无间。而理自理。气自气。亦不相挟杂。故二五与太极。虽曰妙合。而主太极而言。则不杂乎阴阳。人物与性。虽曰不离。而主性而言。则不杂乎气禀。不离不杂之义。如斯而已。而元无天命人物之异矣。今曰天命之不离不杂。非人物性之不离不杂。又曰人性之不离不杂。去天不远。物性之不离不杂。去人犹远。此何谓也。以兄之见。理气不离不杂之说。若是迂阔。深所未晓。
삽화 새창열기
健顺者。性情之分也。所谓几善恶。而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健顺五常。皆当包在心圈中。而今以心与健顺五常。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4L 页
 作三层图之。是可疑。且曰健顺者。性情之分。所谓几善恶。夫健顺。当就五性言。而不可分属于情。且健顺。只以性善之德言。恐不可并比分配于几善恶上也。其下又曰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健顺二字。或可以一阴一阳谓道分配说。岂可以善恶联类混称也。
作三层图之。是可疑。且曰健顺者。性情之分。所谓几善恶。夫健顺。当就五性言。而不可分属于情。且健顺。只以性善之德言。恐不可并比分配于几善恶上也。其下又曰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健顺二字。或可以一阴一阳谓道分配说。岂可以善恶联类混称也。寂然之性。只有生理。故动为健之情。静为顺之情。虽有各偏之名。未及于仁义礼智。而善恶亦无形焉。
静为顺之情云云。此情字若指未发言。则未发上。不可言情。若指已发言。则已发上。亦不可言静矣。且健顺既是纯善。而今曰善恶亦无形。则恐皆未当。且健顺。乃是仁义礼智上分说。今曰未及于仁义礼智。何也。
偏者。偏曲之谓。喜怒哀乐是也。倚者。夫焉有所倚之倚。有一毫私意。则不无思勉之意。不偏不倚。明有分界。
不偏不倚。所论固然。而但所谓不偏不倚明有分界者。似为语病。若曰不偏不倚意义自别则好矣。
浑然则无可分而无不同矣。分而不同则气也情也。非理也。非性也。南塘曰。四者之性。既非相离而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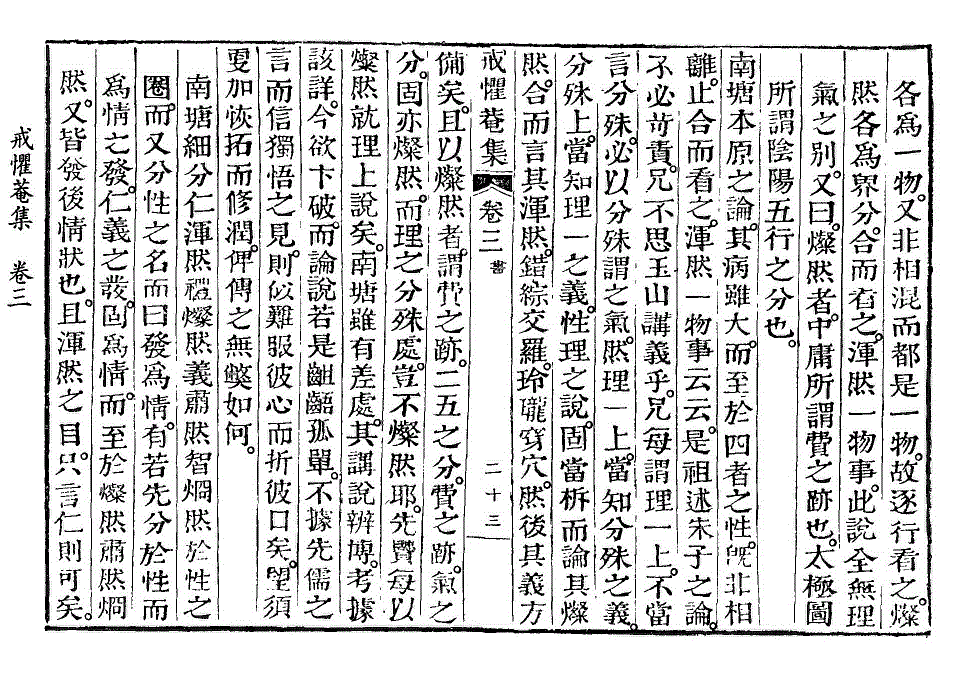 各为一物。又非相混而都是一物。故逐行看之。灿然各为界分。合而看之。浑然一物事。此说全无理气之别。又曰。灿然者。中庸所谓费之迹也。太极图所谓阴阳五行之分也。
各为一物。又非相混而都是一物。故逐行看之。灿然各为界分。合而看之。浑然一物事。此说全无理气之别。又曰。灿然者。中庸所谓费之迹也。太极图所谓阴阳五行之分也。南塘本原之论。其病虽大。而至于四者之性。既非相离。止合而看之。浑然一物事云云。是祖述朱子之论。不必苛责。兄不思玉山讲义乎。兄每谓理一上。不当言分殊。必以分殊谓之气。然理一上。当知分殊之义。分殊上。当知理一之义。性理之说。固当析而论其灿然。合而言其浑然。错综交罗。玲珑穿穴。然后其义方备矣。且以灿然者。谓费之迹。二五之分。费之迹。气之分。固亦灿然。而理之分殊处。岂不灿然耶。先贤每以灿然就理上说矣。南塘虽有差处。其谓说辨博。考据该详。今欲卞破。而论说若是龃龉孤单。不据先儒之言而信独悟之见。则似难服彼心而折彼口矣。望须更加恢拓而修润。俾传之无弊如何。
南塘细分仁浑然礼灿然义肃然智烱然于性之圈。而又分性之名而曰发为情。有若先分于性而为情之发。仁义之发。固为情。而至于灿然肃然烱然。又皆发后情状也。且浑然之目。只言仁则可矣。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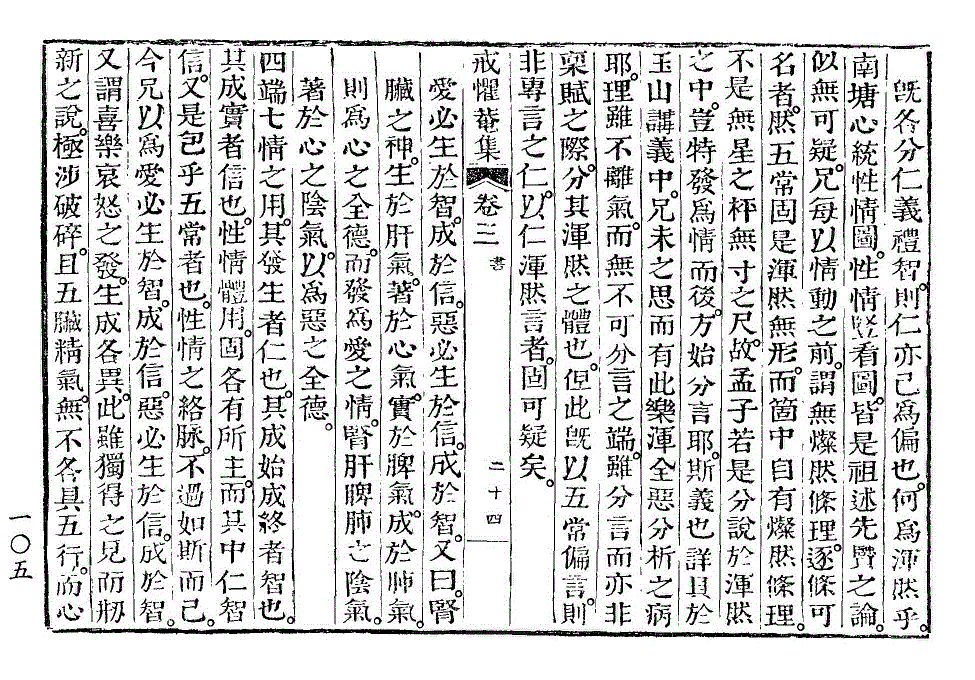 既各分仁义礼智。则仁亦已为偏也。何为浑然乎。
既各分仁义礼智。则仁亦已为偏也。何为浑然乎。南塘心统性情图。性情竖看图。皆是祖述先贤之论。似无可疑。兄每以情动之前。谓无灿然条理。逐条可名者。然五常固是浑然无形。而个中自有灿然条理。不是无星之秤无寸之尺。故孟子若是分说于浑然之中。岂特发为情而后。方始分言耶。斯义也详具于玉山讲义中。兄未之思而有此乐浑全恶分析之病耶。理虽不离气。而无不可分言之端。虽分言而亦非禀赋之际。分其浑然之体也。但此既以五常偏言。则非专言之仁。以仁浑然言者。固可疑矣。
爱必生于智。成于信。恶必生于信。成于智。又曰。肾脏之神。生于肝气。著于心气。实于脾气。成于肺气。则为心之全德。而发为爱之情。肾肝脾肺之阴气。著于心之阴气。以为恶之全德。
四端七情之用。其发生者仁也。其成始成终者智也。其成实者信也。性情体用。固各有所主。而其中仁智信。又是包乎五常者也。性情之络脉。不过如斯而已。今兄以为爱必生于智。成于信。恶必生于信。成于智。又谓喜乐哀怒之发。生成各异。此虽独得之见而刱新之说。极涉破碎。且五脏精气。无不各具五行。而心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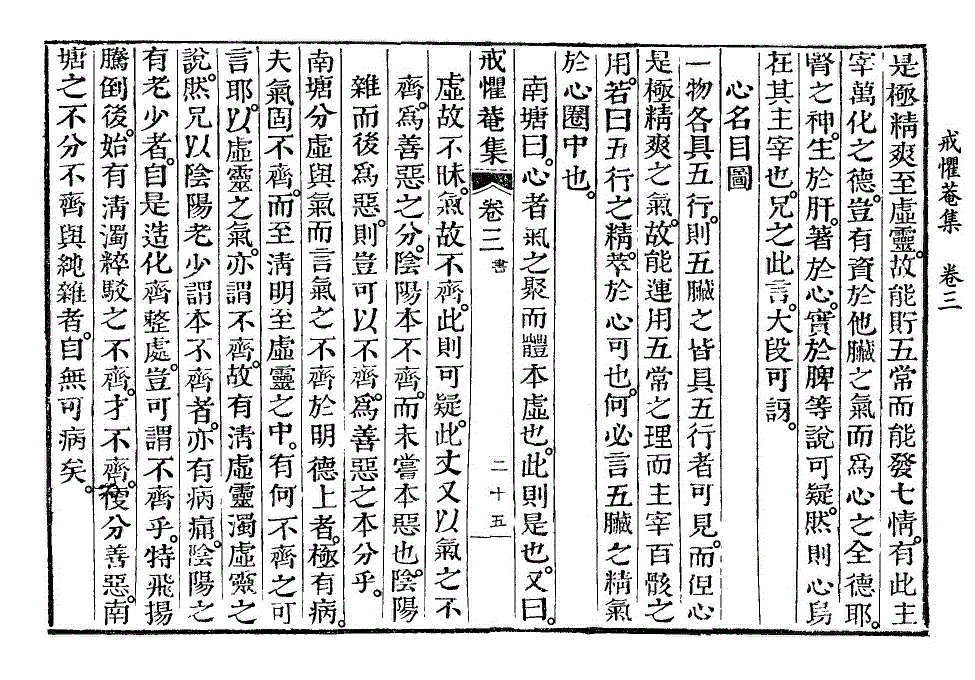 是极精爽至虚灵。故能贮五常而能发七情。有此主宰万化之德。岂有资于他脏之气而为心之全德耶。肾之神。生于肝。著于心。实于脾等说可疑。然则心乌在其主宰也。兄之此言。大段可讶。
是极精爽至虚灵。故能贮五常而能发七情。有此主宰万化之德。岂有资于他脏之气而为心之全德耶。肾之神。生于肝。著于心。实于脾等说可疑。然则心乌在其主宰也。兄之此言。大段可讶。心名目图
一物各具五行。则五脏之皆具五行者可见。而但心是极精爽之气。故能运用五常之理而主宰百骸之用。若曰五行之精。萃于心可也。何必言五脏之精气于心圈中也。
南塘曰。心者气之聚而体本虚也。此则是也。又曰。虚故不昧。气故不齐。此则可疑。此丈又以气之不齐。为善恶之分。阴阳本不齐。而未尝本恶也。阴阳杂而后为恶。则岂可以不齐。为善恶之本分乎。
南塘分虚与气而言气之不齐于明德上者。极有病。夫气固不齐。而至清明至虚灵之中。有何不齐之可言耶。以虚灵之气。亦谓不齐。故有清虚灵浊虚灵之说。然兄以阴阳老少谓本不齐者。亦有病痛。阴阳之有老少者。自是造化齐整处。岂可谓不齐乎。特飞扬腾倒后。始有清浊粹驳之不齐。才不齐。便分善恶。南塘之不分不齐与纯杂者。自无可病矣。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6L 页
 水脏之气。发于心而神明者。其理为智之德。木脏之气。发于心而神明者。其理为仁之德。
水脏之气。发于心而神明者。其理为智之德。木脏之气。发于心而神明者。其理为仁之德。兄于心上。必欲借他脏之气而成全德者。此为刱新之论。其所谓发于此而为德者。未知自他脏而发于心上耶。心不具五行五性。而必资他脏而成全德耶。窃恐此当以五行言之。不必历数五脏而有碍他眼也。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则心本人道之合也。然觉于性命者。为道心而主本然也。觉于形欲者。为人心而主气质也。圣人所以分言者。非为善恶也。明其不可离也。故曰惟精惟一。则心之本体。道与人合而未尝不为一也。
心虽合理气之名。而圣人之分言人心道心。终之以惟一者。非谓人与道之不相离也。特勉其人心之当精察。道心之当固守。而明其为执中之工。且所谓人心。即为形气而发底心。而形气非方寸上合理气之气也。即指耳目口鼻四肢之形气也。今兄不原圣人立言之本意。而错认惟一以为人道合为一之意。忽地以人道不相离之意。搀入主张。故至曰圣人所以分言者。非为善恶也。明其不可离。故曰惟精惟一也。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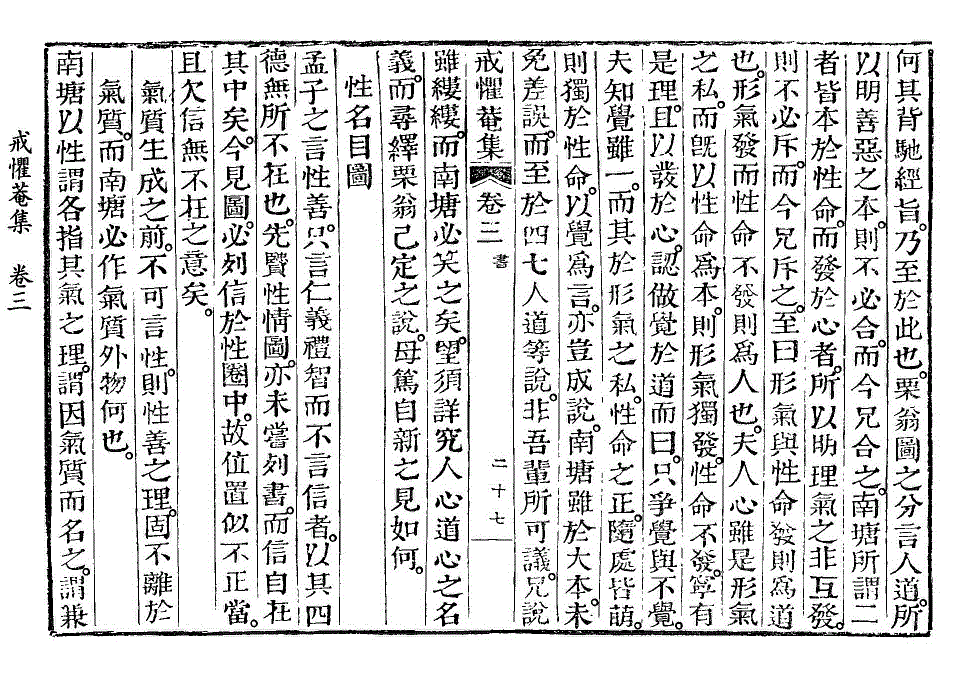 何其背驰经旨。乃至于此也。栗翁图之分言人道。所以明善恶之本。则不必合。而今兄合之。南塘所谓二者皆本于性命。而发于心者。所以明理气之非互发。则不必斥。而今兄斥之。至曰形气与性命发则为道也。形气发而性命不发则为人也。夫人心虽是形气之私。而既以性命为本。则形气独发。性命不发。宁有是理。且以发于心。认做觉于道而曰。只争觉与不觉。夫知觉虽一。而其于形气之私。性命之正。随处皆萌。则独于性命。以觉为言。亦岂成说。南塘虽于大本。未免差误。而至于四七人道等说。非吾辈所可议。兄说虽缕缕。而南塘必笑之矣。望须详究人心道心之名义。而寻绎栗翁已定之说。毋笃自新之见如何。
何其背驰经旨。乃至于此也。栗翁图之分言人道。所以明善恶之本。则不必合。而今兄合之。南塘所谓二者皆本于性命。而发于心者。所以明理气之非互发。则不必斥。而今兄斥之。至曰形气与性命发则为道也。形气发而性命不发则为人也。夫人心虽是形气之私。而既以性命为本。则形气独发。性命不发。宁有是理。且以发于心。认做觉于道而曰。只争觉与不觉。夫知觉虽一。而其于形气之私。性命之正。随处皆萌。则独于性命。以觉为言。亦岂成说。南塘虽于大本。未免差误。而至于四七人道等说。非吾辈所可议。兄说虽缕缕。而南塘必笑之矣。望须详究人心道心之名义。而寻绎栗翁已定之说。毋笃自新之见如何。性名目图
孟子之言性善。只言仁义礼智而不言信者。以其四德无所不在也。先贤性情图。亦未尝列书。而信自在其中矣。今见图。必列信于性圈中。故位置似不正当。且欠信无不在之意矣。
气质生成之前。不可言性。则性善之理。固不离于气质。而南塘必作气质外物何也。
南塘以性谓各指其气之理。谓因气质而名之。谓兼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7L 页
 不杂不离而言。则是不离气质言者也。凡此所言。皆带气质说。南塘之病。政坐不能掉脱形气。而今兄谓南塘必作气质外物。恐失照管。且兄所谓气质生成之前。不可言性者。此即南塘之见。攻斥南塘而反为此等说何也。性者禀受之名。故才说性。不得不带气言。然如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张子所谓性者万物之一原。朱子所谓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之为经纬错综等语。是措气质生成之前。本然不杂气之理。圣贤论性。以本然论者多矣。于此见得。则可以透理一之义。望更详思也。
不杂不离而言。则是不离气质言者也。凡此所言。皆带气质说。南塘之病。政坐不能掉脱形气。而今兄谓南塘必作气质外物。恐失照管。且兄所谓气质生成之前。不可言性者。此即南塘之见。攻斥南塘而反为此等说何也。性者禀受之名。故才说性。不得不带气言。然如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张子所谓性者万物之一原。朱子所谓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之为经纬错综等语。是措气质生成之前。本然不杂气之理。圣贤论性。以本然论者多矣。于此见得。则可以透理一之义。望更详思也。气局之理。虽不更杂。而已局本杂者。为人性为物性。而终非本然之体。
气局中之理。若不杂气而拈出言。则何害为本然。而兄以为终非本然之体何也。南塘则以气局中本然之理。谓之兼不杂不离。而谓之不同。故有病败也。
天命理分图
所谓无全之气无偏之气等语。愚昧之见。终难晓解。天命图无论气之偏全。只曰理全可也。何必言无气耶。未知浑全之理。无气而独存耶。
人物之气。初分天一之数。则全理乘而始生。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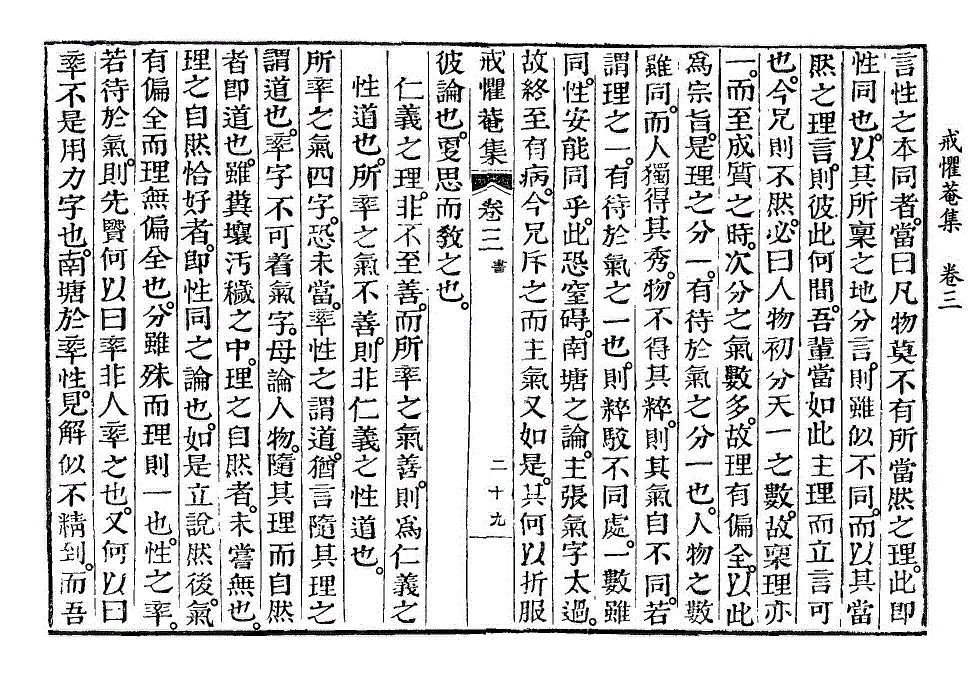 言性之本同者。当曰凡物莫不有所当然之理。此即性同也。以其所禀之地分言。则虽似不同。而以其当然之理言。则彼此何间。吾辈当如此主理而立言可也。今兄则不然。必曰人物初分天一之数。故禀理亦一。而至成质之时。次分之气数多。故理有偏全。以此为宗旨。是理之分一。有待于气之分一也。人物之数虽同。而人独得其秀。物不得其粹。则其气自不同。若谓理之一。有待于气之一也。则粹驳不同处。一数虽同。性安能同乎。此恐窒碍。南塘之论。主张气字太过。故终至有病。今兄斥之而主气又如是。其何以折服彼论也。更思而教之也。
言性之本同者。当曰凡物莫不有所当然之理。此即性同也。以其所禀之地分言。则虽似不同。而以其当然之理言。则彼此何间。吾辈当如此主理而立言可也。今兄则不然。必曰人物初分天一之数。故禀理亦一。而至成质之时。次分之气数多。故理有偏全。以此为宗旨。是理之分一。有待于气之分一也。人物之数虽同。而人独得其秀。物不得其粹。则其气自不同。若谓理之一。有待于气之一也。则粹驳不同处。一数虽同。性安能同乎。此恐窒碍。南塘之论。主张气字太过。故终至有病。今兄斥之而主气又如是。其何以折服彼论也。更思而教之也。仁义之理。非不至善。而所率之气善。则为仁义之性道也。所率之气不善。则非仁义之性道也。
所率之气四字。恐未当。率性之谓道。犹言随其理之谓道也。率字不可着气字。毋论人物。随其理而自然者即道也。虽粪壤污秽之中。理之自然者。未尝无也。理之自然恰好者。即性同之论也。如是立说然后。气有偏全而理无偏全也。分虽殊而理则一也。性之率。若待于气。则先贤何以曰率非人率之也。又何以曰率不是用力字也。南塘于率性。见解似不精到。而吾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8L 页
 兄所率之气云云。亦未通透矣。如何。
兄所率之气云云。亦未通透矣。如何。南塘曰。人物本性之不同。只争其偏全。而不当争其善不善也。此尤未解也。
或问于朱子曰。物各具一太极。是理无不全。曰。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以理言之。无不全。以气言之。不能无偏。窃谓以其粗通一路言则固偏矣。而言其纯善则本全也。故谓之偏亦可。谓之全亦可。南塘则主偏而未知其全。吾兄则主全而过斥其偏。幸思其偏之不必以恶言之如何。
朱子释生之谓性之生字曰。指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则所以者知觉运动之理也。
朱子训释生之谓性曰。生指所以知觉运动者言。所以二字。即指生字言。夫生字气也。兄何以曰所以知觉运动之理也。恐偶失照管矣。
四端者。性情分属。定位不易者也。七情。健顺互发之四端也。实则未尝不同。而以互发之情。分属定位之名目。脉络拘碍。
以四端分属七情。明有栗谷说。亦何以为误。且性情各有攸主。而五性又互主乎四者云云。南塘图说。皆祖朱子说。如兄所谓情路各有健顺次第。亦似刱新。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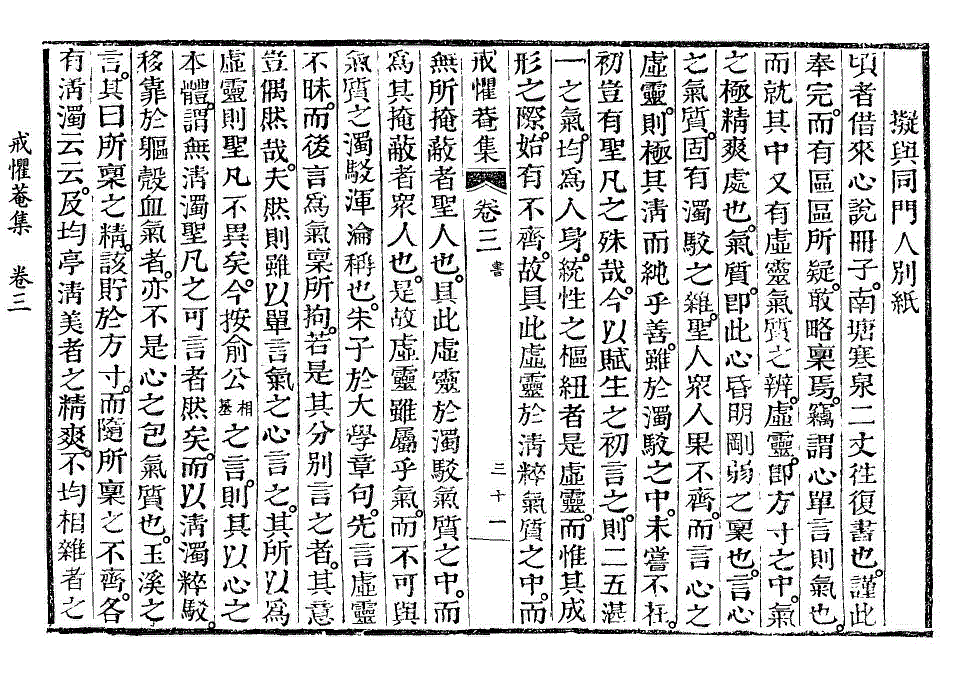 拟与同门人别纸
拟与同门人别纸顷者借来心说册子。南塘寒泉二丈往复书也。谨此奉完。而有区区所疑。敢略禀焉。窃谓心单言则气也。而就其中又有虚灵气质之辨。虚灵。即方寸之中。气之极精爽处也。气质。即此心昏明刚弱之禀也。言心之气质。固有浊驳之杂。圣人众人果不齐。而言心之虚灵。则极其清而纯乎善。虽于浊驳之中。未尝不在。初岂有圣凡之殊哉。今以赋生之初言之。则二五湛一之气。均为人身。统性之枢纽者是虚灵。而惟其成形之际。始有不齐。故具此虚灵于清粹气质之中。而无所掩蔽者圣人也。具此虚灵于浊驳气质之中。而为其掩蔽者众人也。是故虚灵虽属乎气。而不可与气质之浊驳浑沦称也。朱子于大学章句。先言虚灵不昧。而后言为气禀所拘。若是其分别言之者。其意岂偶然哉。夫然则虽以单言气之心言之。其所以为虚灵则圣凡不异矣。今按俞公(相基)之言。则其以心之本体。谓无清浊圣凡之可言者然矣。而以清浊粹驳。移靠于躯壳血气者。亦不是心之包气质也。玉溪之言。其曰所禀之精。该贮于方寸。而随所禀之不齐。各有清浊云云。及均亭清美者之精爽。不均相杂者之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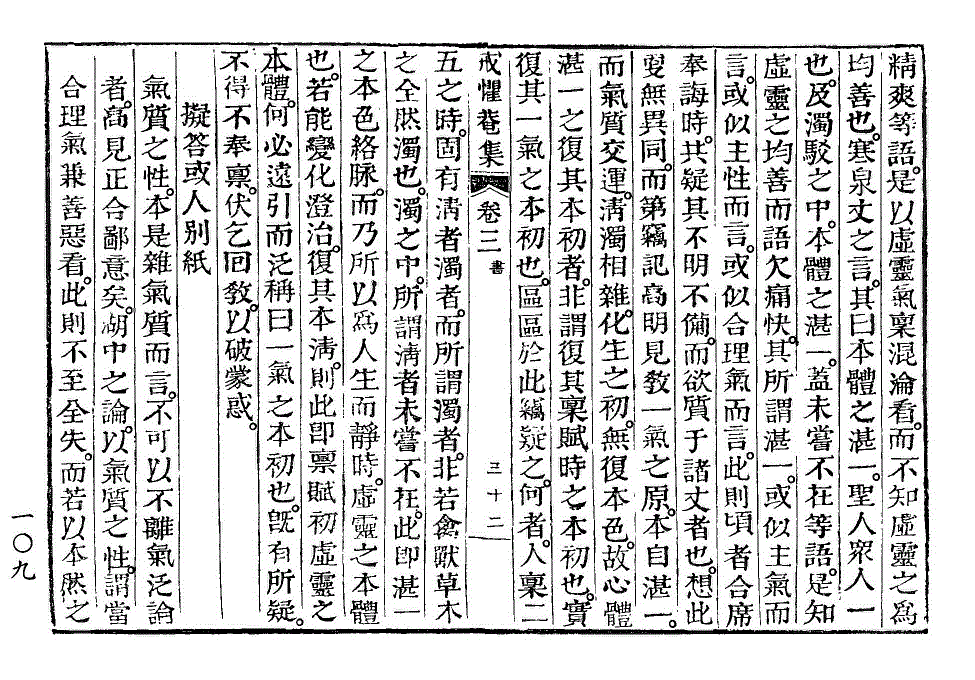 精爽等语。是以虚灵气禀混沦看。而不知虚灵之为均善也。寒泉丈之言。其曰本体之湛一。圣人众人一也。及浊驳之中。本体之湛一。盖未尝不在等语。是知虚灵之均善而语欠痛快。其所谓湛一。或似主气而言。或似主性而言。或似合理气而言。此则顷者合席奉诲时。共疑其不明不备。而欲质于诸丈者也。想此更无异同。而第窃记高明见教一气之原。本自湛一。而气质交运。清浊相杂。化生之初。无复本色。故心体湛一之复其本初者。非谓复其禀赋时之本初也。实复其一气之本初也。区区于此窃疑之。何者。人禀二五之时。固有清者浊者。而所谓浊者。非若禽兽草木之全然浊也。浊之中。所谓清者未尝不在。此即湛一之本色络脉。而乃所以为人生而静时。虚灵之本体也。若能变化澄治。复其本清。则此即禀赋初虚灵之本体。何必远引而泛称曰一气之本初也。既有所疑。不得不奉禀。伏乞回教。以破蒙惑。
精爽等语。是以虚灵气禀混沦看。而不知虚灵之为均善也。寒泉丈之言。其曰本体之湛一。圣人众人一也。及浊驳之中。本体之湛一。盖未尝不在等语。是知虚灵之均善而语欠痛快。其所谓湛一。或似主气而言。或似主性而言。或似合理气而言。此则顷者合席奉诲时。共疑其不明不备。而欲质于诸丈者也。想此更无异同。而第窃记高明见教一气之原。本自湛一。而气质交运。清浊相杂。化生之初。无复本色。故心体湛一之复其本初者。非谓复其禀赋时之本初也。实复其一气之本初也。区区于此窃疑之。何者。人禀二五之时。固有清者浊者。而所谓浊者。非若禽兽草木之全然浊也。浊之中。所谓清者未尝不在。此即湛一之本色络脉。而乃所以为人生而静时。虚灵之本体也。若能变化澄治。复其本清。则此即禀赋初虚灵之本体。何必远引而泛称曰一气之本初也。既有所疑。不得不奉禀。伏乞回教。以破蒙惑。拟答或人别纸
气质之性。本是杂气质而言。不可以不离气泛论者。高见正合鄙意矣。湖中之论。以气质之性。谓当合理气兼善恶看。此则不至全失。而若以本然之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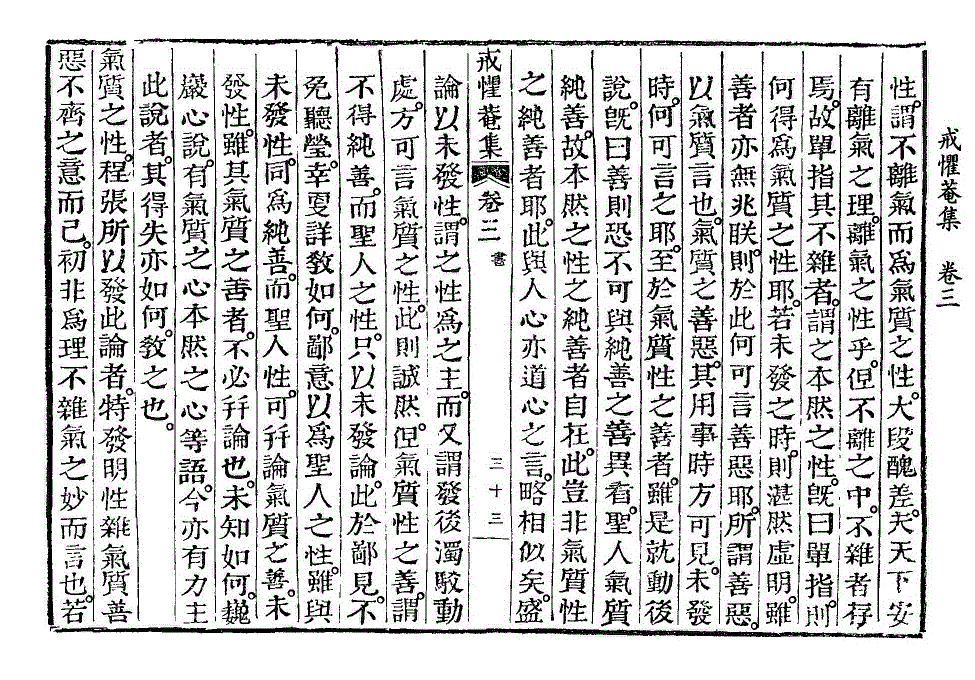 性。谓不离气而为气质之性。大段丑差。夫天下安有离气之理。离气之性乎。但不离之中。不杂者存焉。故单指其不杂者。谓之本然之性。既曰单指。则何得为气质之性耶。若未发之时。则湛然虚明。虽善者亦无兆眹。则于此何可言善恶耶。所谓善恶。以气质言也。气质之善恶。其用事时方可见。未发时。何可言之耶。至于气质性之善者。虽是就动后说。既曰善则恐不可与纯善之善异看。圣人气质纯善。故本然之性之纯善者自在。此岂非气质性之纯善者耶。此与人心亦道心之言。略相似矣。盛论以未发性。谓之性为之主。而又谓发后浊驳动处。方可言气质之性。此则诚然。但气质性之善。谓不得纯善。而圣人之性。只以未发论。此于鄙见。不免听莹。幸更详教如何。鄙意以为圣人之性。虽与未发性。同为纯善。而圣人性。可并论气质之善。未发性。虽其气质之善者。不必并论也。未知如何。巍岩心说。有气质之心本然之心等语。今亦有力主此说者。其得失亦如何。教之也。
性。谓不离气而为气质之性。大段丑差。夫天下安有离气之理。离气之性乎。但不离之中。不杂者存焉。故单指其不杂者。谓之本然之性。既曰单指。则何得为气质之性耶。若未发之时。则湛然虚明。虽善者亦无兆眹。则于此何可言善恶耶。所谓善恶。以气质言也。气质之善恶。其用事时方可见。未发时。何可言之耶。至于气质性之善者。虽是就动后说。既曰善则恐不可与纯善之善异看。圣人气质纯善。故本然之性之纯善者自在。此岂非气质性之纯善者耶。此与人心亦道心之言。略相似矣。盛论以未发性。谓之性为之主。而又谓发后浊驳动处。方可言气质之性。此则诚然。但气质性之善。谓不得纯善。而圣人之性。只以未发论。此于鄙见。不免听莹。幸更详教如何。鄙意以为圣人之性。虽与未发性。同为纯善。而圣人性。可并论气质之善。未发性。虽其气质之善者。不必并论也。未知如何。巍岩心说。有气质之心本然之心等语。今亦有力主此说者。其得失亦如何。教之也。气质之性。程张所以发此论者。特发明性杂气质善恶不齐之意而已。初非为理不杂气之妙而言也。若
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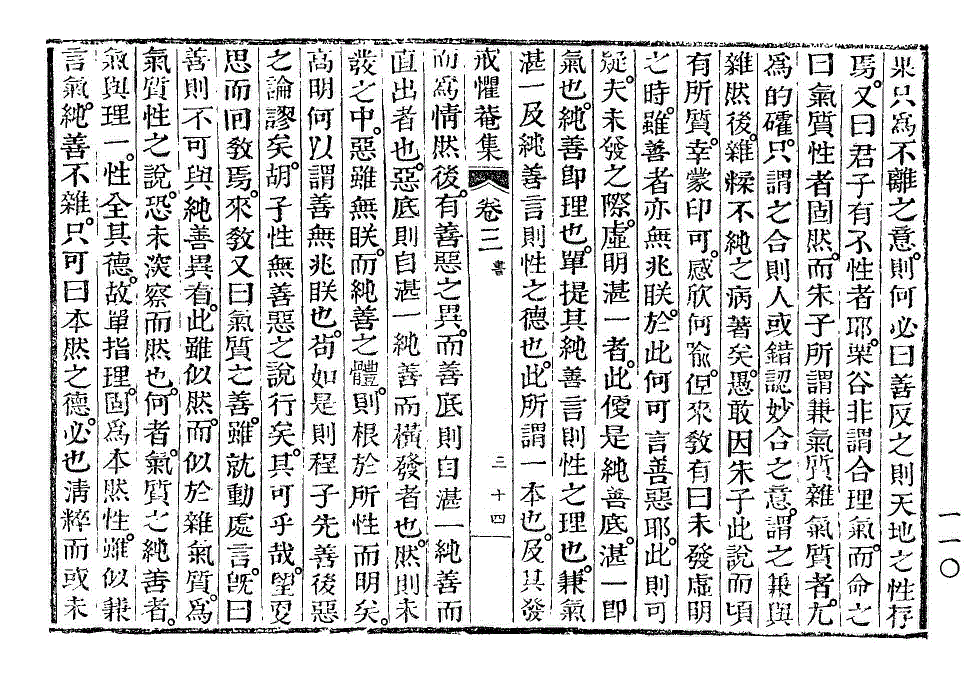 果只为不离之意。则何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君子有不性者耶。栗谷非谓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性者固然。而朱子所谓兼气质杂气质者。尤为的礭。只谓之合则人或错认妙合之意。谓之兼与杂然后。杂糅不纯之病著矣。愚敢因朱子此说而顷有所质。幸蒙印可。感欣何喻。但来教有曰未发虚明之时。虽善者亦无兆眹。于此何可言善恶耶。此则可疑。夫未发之际。虚明湛一者。此便是纯善底。湛一即气也。纯善即理也。单提其纯善言则性之理也。兼气湛一及纯善言则性之德也。此所谓一本也。及其发而为情然后。有善恶之异。而善底则自湛一纯善而直出者也。恶底则自湛一纯善而横发者也。然则未发之中。恶虽无眹。而纯善之体。则根于所性而明矣。高明何以谓善无兆眹也。苟如是则程子先善后恶之论谬矣。胡子性无善恶之说行矣。其可乎哉。望更思而回教焉。来教又曰气质之善。虽就动处言。既曰善则不可与纯善异看。此虽似然。而似于杂气质。为气质性之说。恐未深察而然也。何者。气质之纯善者。气与理一。性全其德。故单指理。固为本然性。虽似兼言气。纯善不杂。只可曰本然之德。必也清粹而或未
果只为不离之意。则何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君子有不性者耶。栗谷非谓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性者固然。而朱子所谓兼气质杂气质者。尤为的礭。只谓之合则人或错认妙合之意。谓之兼与杂然后。杂糅不纯之病著矣。愚敢因朱子此说而顷有所质。幸蒙印可。感欣何喻。但来教有曰未发虚明之时。虽善者亦无兆眹。于此何可言善恶耶。此则可疑。夫未发之际。虚明湛一者。此便是纯善底。湛一即气也。纯善即理也。单提其纯善言则性之理也。兼气湛一及纯善言则性之德也。此所谓一本也。及其发而为情然后。有善恶之异。而善底则自湛一纯善而直出者也。恶底则自湛一纯善而横发者也。然则未发之中。恶虽无眹。而纯善之体。则根于所性而明矣。高明何以谓善无兆眹也。苟如是则程子先善后恶之论谬矣。胡子性无善恶之说行矣。其可乎哉。望更思而回教焉。来教又曰气质之善。虽就动处言。既曰善则不可与纯善异看。此虽似然。而似于杂气质。为气质性之说。恐未深察而然也。何者。气质之纯善者。气与理一。性全其德。故单指理。固为本然性。虽似兼言气。纯善不杂。只可曰本然之德。必也清粹而或未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11H 页
 纯。浊驳而或相杂。性有所杂。善恶不齐者。然后方可谓气质性。故虽有善者。而其善亦未纯乎善矣。今高明于气质性善恶不齐之善字。看做纯善之意。若然则气质性是半边为本然纯善之性。程子何以善反不性等语驳之耶。朱子于通书注。论气质性之善恶而曰。恶者固为非正。而其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斯言岂欺我哉。望更俯量而砭示焉。来教又曰圣人性。可并论气质之善。未发性。虽气质之善者。不必并论。此亦有可以奉质者。盛意无乃以为气质性。是就动处说。而未发只举静一边言。圣人言动静之德。故并论气之善。有异同耶。愚意则圣人之清粹。未发之湛一。俱是本然纯善之气。而未发之境。即圣人之静。则本然纯善之气。岂有异同也。但气质之性。是气之动处。性有所杂。不纯乎善者。故圣人分上未发地头。俱不可言之矣。亦望回教如何。大抵气质性。不当以合理气泛称。而惟以杂气不性之性细究。则自馀疑端。不卞而释矣。更须于此细加思议如何。湖中之论。每以此性对情言。而归之静一边。泛做不离气之义。而不属于已发地头。故许多病败。皆由于斯。此诚大本肯綮。而今世无可与质此者。今幸与高明发此议
纯。浊驳而或相杂。性有所杂。善恶不齐者。然后方可谓气质性。故虽有善者。而其善亦未纯乎善矣。今高明于气质性善恶不齐之善字。看做纯善之意。若然则气质性是半边为本然纯善之性。程子何以善反不性等语驳之耶。朱子于通书注。论气质性之善恶而曰。恶者固为非正。而其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斯言岂欺我哉。望更俯量而砭示焉。来教又曰圣人性。可并论气质之善。未发性。虽气质之善者。不必并论。此亦有可以奉质者。盛意无乃以为气质性。是就动处说。而未发只举静一边言。圣人言动静之德。故并论气之善。有异同耶。愚意则圣人之清粹。未发之湛一。俱是本然纯善之气。而未发之境。即圣人之静。则本然纯善之气。岂有异同也。但气质之性。是气之动处。性有所杂。不纯乎善者。故圣人分上未发地头。俱不可言之矣。亦望回教如何。大抵气质性。不当以合理气泛称。而惟以杂气不性之性细究。则自馀疑端。不卞而释矣。更须于此细加思议如何。湖中之论。每以此性对情言。而归之静一边。泛做不离气之义。而不属于已发地头。故许多病败。皆由于斯。此诚大本肯綮。而今世无可与质此者。今幸与高明发此议戒惧庵集卷之三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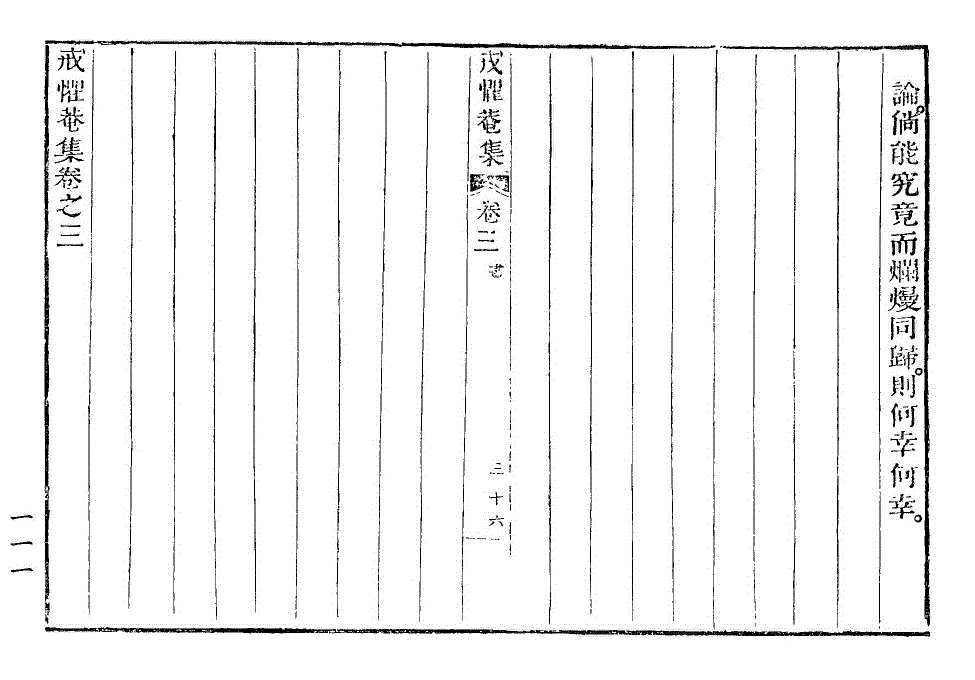 论。倘能究竟而烂熳同归。则何幸何幸。
论。倘能究竟而烂熳同归。则何幸何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