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x 页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杂著
杂著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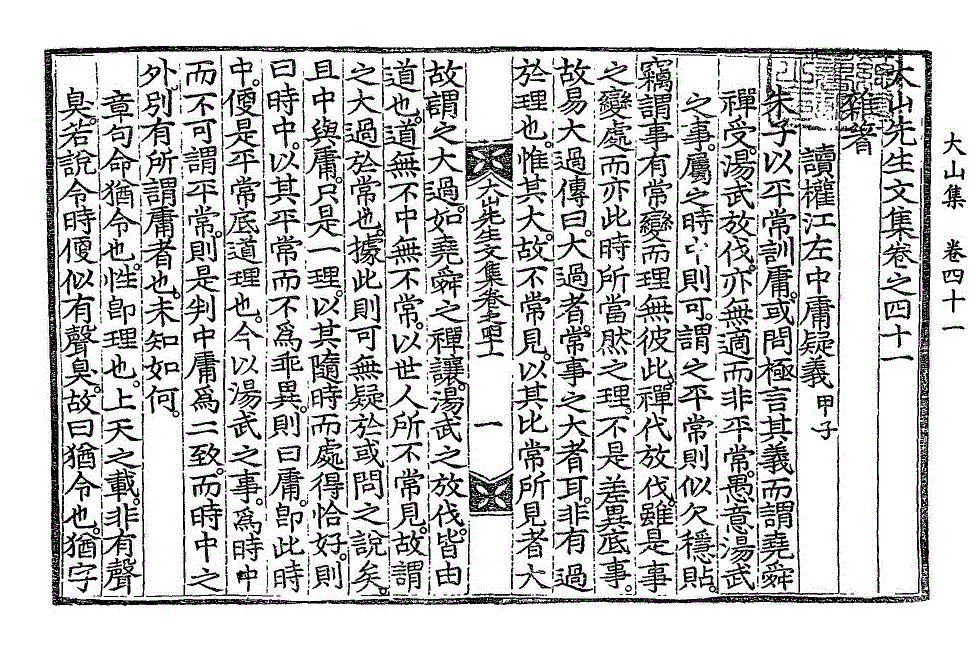 读权江左中庸疑义(甲子)
读权江左中庸疑义(甲子)朱子以平常训庸。或问极言其义而谓尧舜禅受。汤武放伐。亦无适而非平常。愚意汤武之事。属之时中则可。谓之平常则似欠稳贴。
窃谓事有常变而理无彼此。禅代放伐。虽是事之变处而亦此时所当然之理。不是差异底事。故易大过传曰。大过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过于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见。以其比常所见者大故谓之大过。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见。故谓之大过于常也。据此则可无疑于或问之说矣。且中与庸。只是一理。以其随时而处得恰好。则曰时中。以其平常而不为乖异。则曰庸。即此时中。便是平常底道理也。今以汤武之事。为时中而不可谓平常。则是判中庸为二致。而时中之外。别有所谓庸者也。未知如何。
章句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上天之载。非有声臭。若说令时便似有声臭。故曰犹令也。犹字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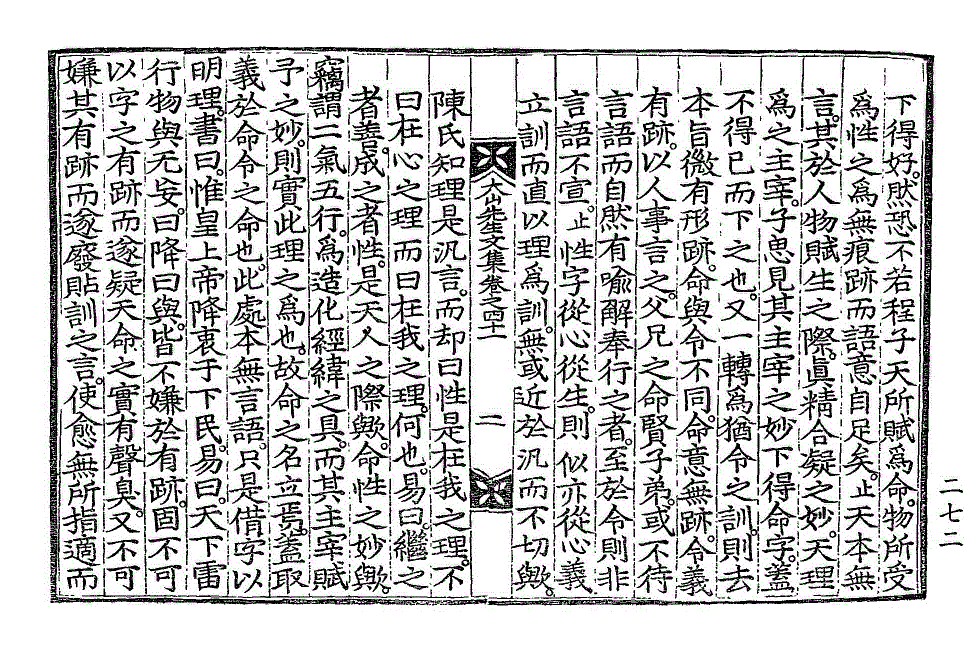 下得好。然恐不若程子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之为无痕迹而语意自足矣。(止)天本无言。其于人物赋生之际。真精合凝之妙。天理为之主宰。子思见其主宰之妙下得命字。盖不得已而下之也。又一转为犹令之训。则去本旨微有形迹。命与令不同。命意无迹。令义有迹。以人事言之。父兄之命贤子弟。或不待言语而自然有喻解奉行之者。至于令则非言语不宣。(止)性字从心从生。则似亦从心义立训而直以理为训。无或近于汎而不切欤。陈氏知理是汎言。而却曰性是在我之理。不曰在心之理而曰在我之理。何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人之际欤。命性之妙欤。
下得好。然恐不若程子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之为无痕迹而语意自足矣。(止)天本无言。其于人物赋生之际。真精合凝之妙。天理为之主宰。子思见其主宰之妙下得命字。盖不得已而下之也。又一转为犹令之训。则去本旨微有形迹。命与令不同。命意无迹。令义有迹。以人事言之。父兄之命贤子弟。或不待言语而自然有喻解奉行之者。至于令则非言语不宣。(止)性字从心从生。则似亦从心义立训而直以理为训。无或近于汎而不切欤。陈氏知理是汎言。而却曰性是在我之理。不曰在心之理而曰在我之理。何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人之际欤。命性之妙欤。窃谓二气五行。为造化经纬之具。而其主宰赋予之妙。则实此理之为也。故命之名立焉。盖取义于命令之命也。此处本无言语。只是借字以明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易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曰降曰与。皆不嫌于有迹。固不可以字之有迹而遂疑天命之实有声臭。又不可嫌其有迹而遂废贴训之言。使愈无所指适而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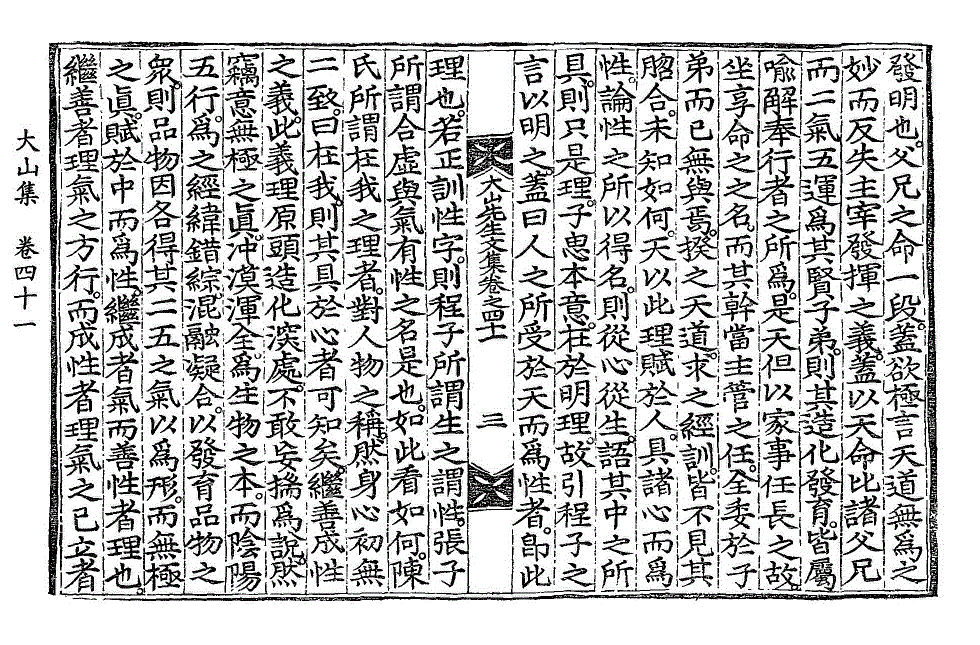 发明也。父兄之命一段。盖欲极言天道无为之妙而反失主宰发挥之义。盖以天命比诸父兄而二气五运为其贤子弟。则其造化发育。皆属喻解奉行者之所为。是天但以家事任长之故。坐享命之之名。而其干当主管之任。全委于子弟而已无与焉。揆之天道。求之经训。皆不见其吻合。未知如何。天以此理赋于人。具诸心而为性。论性之所以得名。则从心从生。语其中之所具。则只是理。子思本意。在于明理。故引程子之言以明之。盖曰人之所受于天而为性者。即此理也。若正训性字。则程子所谓生之谓性。张子所谓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是也。如此看如何。陈氏所谓在我之理者。对人物之称。然身心初无二致。曰在我。则其具于心者可知矣。继善成性之义。此义理原头造化深处。不敢妄揣为说。然窃意无极之真。冲漠浑全。为生物之本。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混融凝合。以发育品物之众。则品物因各得其二五之气以为形。而无极之真。赋于中而为性。继成者气而善性者理也。继善者理气之方行。而成性者理气之已立者
发明也。父兄之命一段。盖欲极言天道无为之妙而反失主宰发挥之义。盖以天命比诸父兄而二气五运为其贤子弟。则其造化发育。皆属喻解奉行者之所为。是天但以家事任长之故。坐享命之之名。而其干当主管之任。全委于子弟而已无与焉。揆之天道。求之经训。皆不见其吻合。未知如何。天以此理赋于人。具诸心而为性。论性之所以得名。则从心从生。语其中之所具。则只是理。子思本意。在于明理。故引程子之言以明之。盖曰人之所受于天而为性者。即此理也。若正训性字。则程子所谓生之谓性。张子所谓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是也。如此看如何。陈氏所谓在我之理者。对人物之称。然身心初无二致。曰在我。则其具于心者可知矣。继善成性之义。此义理原头造化深处。不敢妄揣为说。然窃意无极之真。冲漠浑全。为生物之本。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混融凝合。以发育品物之众。则品物因各得其二五之气以为形。而无极之真。赋于中而为性。继成者气而善性者理也。继善者理气之方行。而成性者理气之已立者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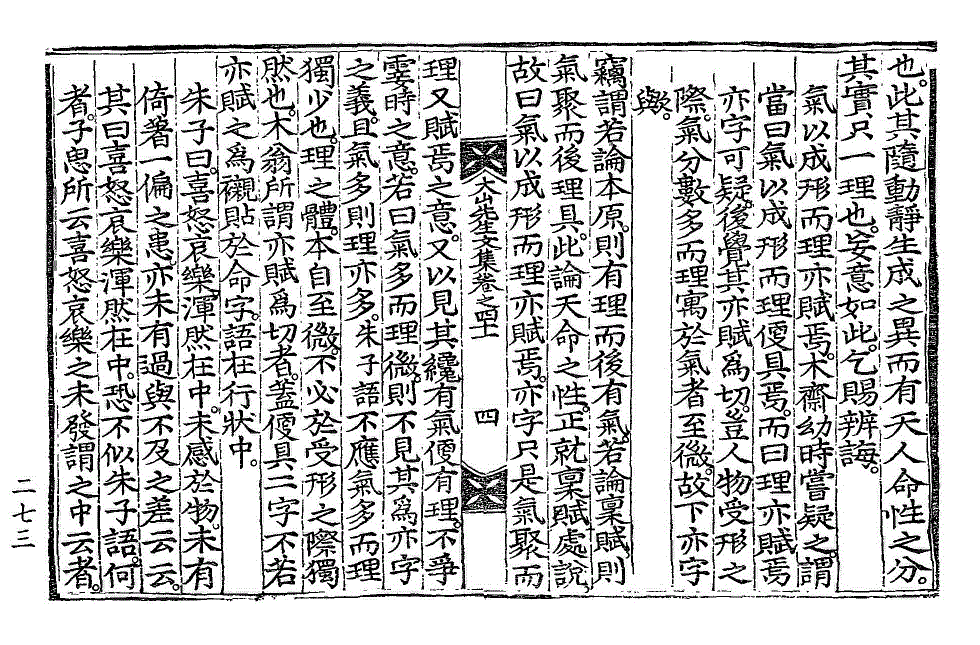 也。此其随动静生成之异而有天人命性之分。其实只一理也。妄意如此。乞赐辨诲。
也。此其随动静生成之异而有天人命性之分。其实只一理也。妄意如此。乞赐辨诲。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木斋幼时尝疑之。谓当曰气以成形而理便具焉。而曰理亦赋焉亦字可疑。后觉其亦赋为切。岂人物受形之际。气分数多而理寓于气者至微。故下亦字欤。
窃谓若论本原。则有理而后有气。若论禀赋。则气聚而后理具。此论天命之性。正就禀赋处说。故曰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亦字只是气聚而理又赋焉之意。又以见其才有气便有理。不争霎时之意。若曰气多而理微。则不见其为亦字之义。且气多则理亦多。(朱子语。)不应气多而理独少也。理之体。本自至微。不必于受形之际独然也。木翁所谓亦赋为切者。盖便具二字不若亦赋之为衬贴于命字。语在行状中。
朱子曰。喜怒哀乐。浑然在中。未感于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过与不及之差云云。其曰喜怒哀乐浑然在中。恐不似朱子语。何者。子思所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云者。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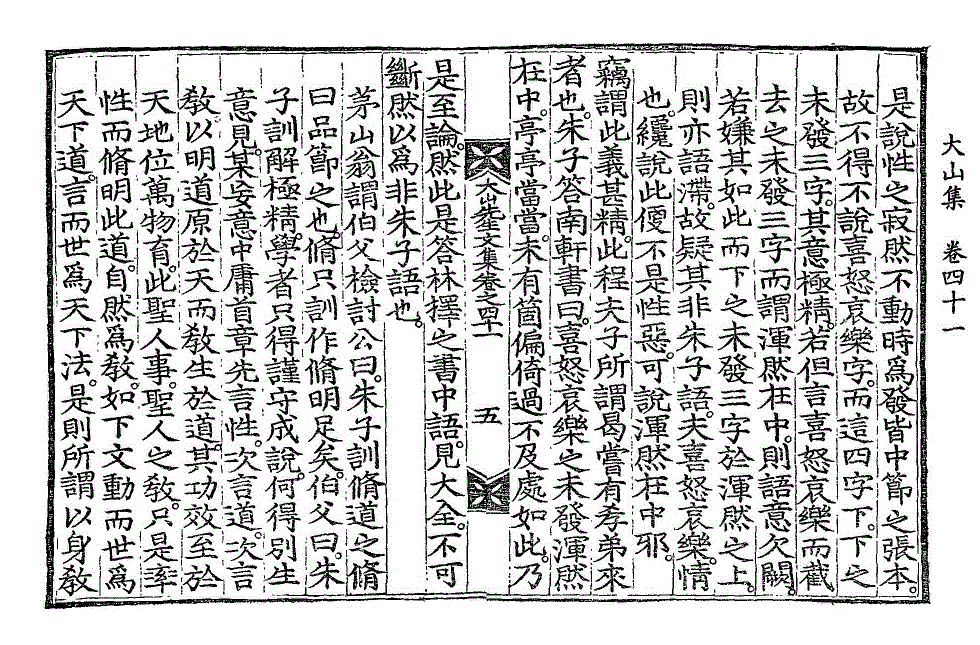 是说性之寂然不动时为发皆中节之张本。故不得不说喜怒哀乐字。而这四字下。下之未发三字。其意极精。若但言喜怒哀乐而截去之未发三字而谓浑然在中。则语意欠阙。若嫌其如此而下之未发三字于浑然之上。则亦语滞。故疑其非朱子语。夫喜怒哀乐。情也。才说此便不是性恶。可说浑然在中邪。
是说性之寂然不动时为发皆中节之张本。故不得不说喜怒哀乐字。而这四字下。下之未发三字。其意极精。若但言喜怒哀乐而截去之未发三字而谓浑然在中。则语意欠阙。若嫌其如此而下之未发三字于浑然之上。则亦语滞。故疑其非朱子语。夫喜怒哀乐。情也。才说此便不是性恶。可说浑然在中邪。窃谓此义甚精。此程夫子所谓曷尝有孝弟来者也。朱子答南轩书曰。喜怒哀乐之未发浑然在中。亭亭当当。未有个偏倚过不及处如此。乃是至论。然此是答林择之书中语。见大全。不可断然以为非朱子语也。
茅山翁谓伯父检讨公曰。朱子训脩道之脩曰品节之也。脩只训作脩明足矣。伯父曰。朱子训解极精。学者只得谨守成说。何得别生意见。某妄意中庸首章先言性。次言道。次言教。以明道原于天而教生于道。其功效至于天地位万物育。此圣人事。圣人之教。只是率性而脩明此道。自然为教。如下文动而世为天下道。言而世为天下法。是则所谓以身教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4L 页
 者也。如曰品节之而以礼乐刑政之属言之。则似有多少节目。下虽言因吾所固有之道而裁之。然才说裁字。煞有人为底意思。故茅翁疑之欤。(止)朱子之意。以为率性云者。率循天理之正。自然为道。方是道。若容人为。便不是道。率与脩。虽有次序。而率性既不容人为。则脩时又岂容多少人为欤。(止)无固无必者。圣人也。若有意传后而脩道立教则为己。君子之所不为而圣人为之哉。朱子曰。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谓之教者。诚是矣。训首章脩道之脩。则以为法三字。亦似微有人为底意思欤。戒慎恐惧。朱子谓不须说得太重。只是略略收拾来。此言圣人与天同德。天不息则圣人亦无息。无事于大煞操存。如学者之用工。特遵循自有之性而略略收拾来云尔。何独至于脩道立教而大煞著力邪。(止)礼乐是圣人日用。无非礼乐。若刑政。辅治之具。遽言于首章性道教之下。终不能无疑。(止)如谓天下义理。岂朱子独知而我不能知云尔。则诚妄矣。笃信朱子
者也。如曰品节之而以礼乐刑政之属言之。则似有多少节目。下虽言因吾所固有之道而裁之。然才说裁字。煞有人为底意思。故茅翁疑之欤。(止)朱子之意。以为率性云者。率循天理之正。自然为道。方是道。若容人为。便不是道。率与脩。虽有次序。而率性既不容人为。则脩时又岂容多少人为欤。(止)无固无必者。圣人也。若有意传后而脩道立教则为己。君子之所不为而圣人为之哉。朱子曰。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谓之教者。诚是矣。训首章脩道之脩。则以为法三字。亦似微有人为底意思欤。戒慎恐惧。朱子谓不须说得太重。只是略略收拾来。此言圣人与天同德。天不息则圣人亦无息。无事于大煞操存。如学者之用工。特遵循自有之性而略略收拾来云尔。何独至于脩道立教而大煞著力邪。(止)礼乐是圣人日用。无非礼乐。若刑政。辅治之具。遽言于首章性道教之下。终不能无疑。(止)如谓天下义理。岂朱子独知而我不能知云尔。则诚妄矣。笃信朱子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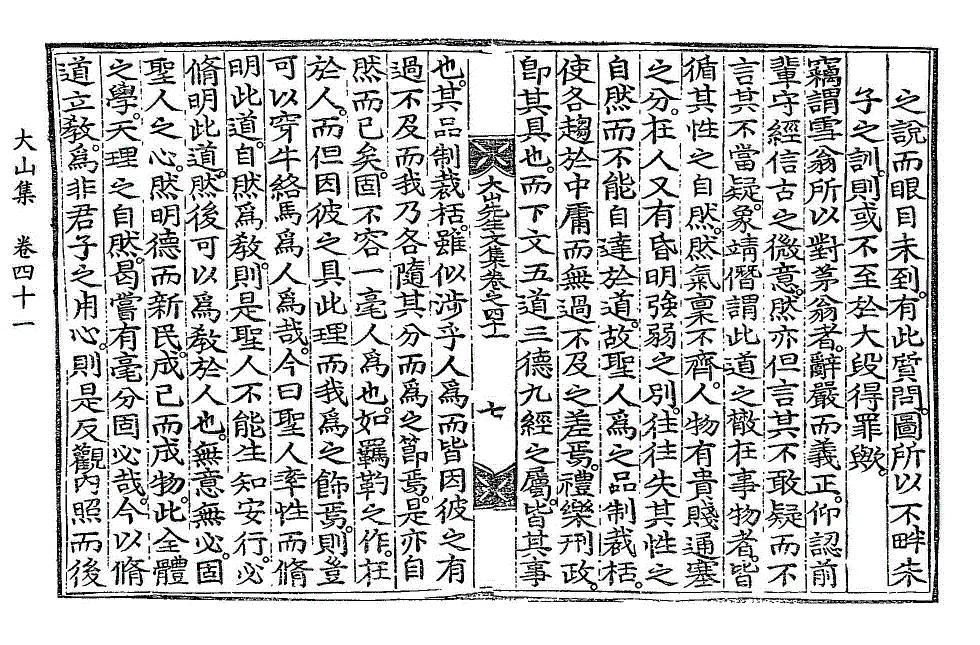 之说而眼目未到。有此质问。图所以不畔朱子之训。则或不至于大段得罪欤。
之说而眼目未到。有此质问。图所以不畔朱子之训。则或不至于大段得罪欤。窃谓雪翁所以对茅翁者。辞严而义正。仰认前辈守经信古之微意。然亦但言其不敢疑而不言其不当疑。象靖僭谓此道之散在事物者。皆循其性之自然。然气禀不齐。人物有贵贱通塞之分。在人又有昏明强弱之别。往往失其性之自然而不能自达于道。故圣人为之品制裁栝。使各趋于中庸而无过不及之差焉。礼乐刑政。即其具也。而下文五道三德九经之属。皆其事也。其品制裁栝。虽似涉乎人为而皆因彼之有过不及而我乃各随其分而为之节焉。是亦自然而已矣。固不容一毫人为也。如羁靮之作。在于人。而但因彼之具此理而我为之饰焉。则岂可以穿牛络马为人为哉。今曰圣人率性而脩明此道。自然为教。则是圣人不能生知安行。必脩明此道。然后可以为教于人也。无意无必。固圣人之心。然明德而新民。成己而成物。此全体之学。天理之自然。曷尝有毫分固必哉。今以脩道立教。为非君子之用心。则是反观内照而后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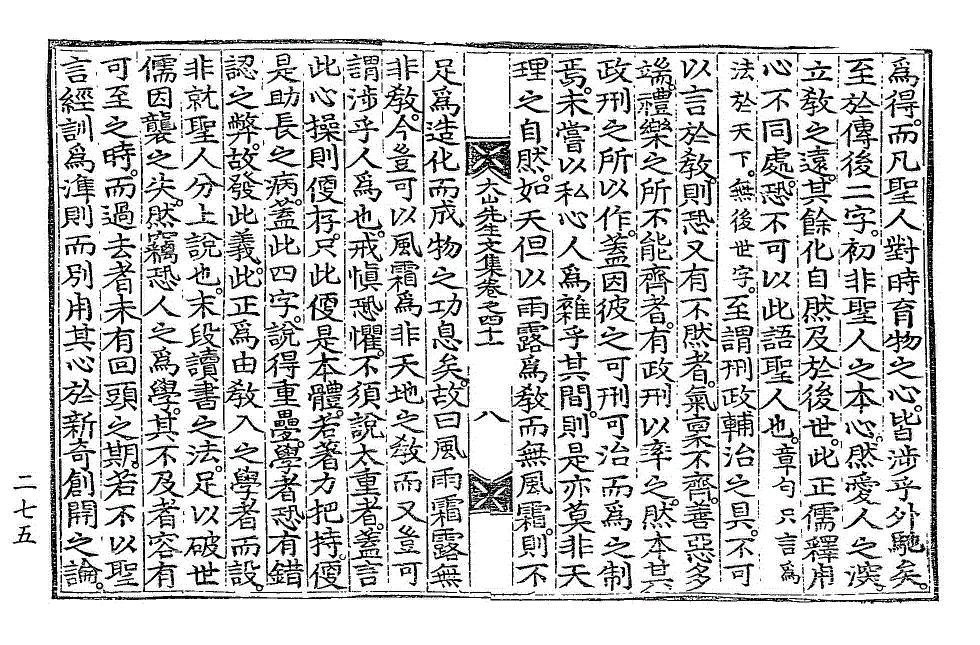 为得。而凡圣人对时育物之心。皆涉乎外驰矣。至于传后二字。初非圣人之本心。然爱人之深。立教之远。其馀化自然及于后世。此正儒释用心不同处。恐不可以此语圣人也。(章句只言为法于天下。无后世字。)至谓刑政辅治之具。不可以言于教。则恐又有不然者。气禀不齐。善恶多端。礼乐之所不能齐者。有政刑以率之。然本其政刑之所以作。盖因彼之可刑可治而为之制焉。未尝以私心人为杂乎其间。则是亦莫非天理之自然。如天但以雨露为教而无风霜。则不足为造化而成物之功息矣。故曰风雨霜露无非教。今岂可以风霜为非天地之教而又岂可谓涉乎人为也。戒慎恐惧。不须说太重者。盖言此心操则便存。只此便是本体。若著力把持。便是助长之病。盖此四字。说得重叠。学者恐有错认之弊。故发此义。此正为由教入之学者而设。非就圣人分上说也。末段读书之法。足以破世儒因袭之失。然窃恐人之为学。其不及者容有可至之时。而过去者未有回头之期。若不以圣言经训为准则而别用其心于新奇创开之论。
为得。而凡圣人对时育物之心。皆涉乎外驰矣。至于传后二字。初非圣人之本心。然爱人之深。立教之远。其馀化自然及于后世。此正儒释用心不同处。恐不可以此语圣人也。(章句只言为法于天下。无后世字。)至谓刑政辅治之具。不可以言于教。则恐又有不然者。气禀不齐。善恶多端。礼乐之所不能齐者。有政刑以率之。然本其政刑之所以作。盖因彼之可刑可治而为之制焉。未尝以私心人为杂乎其间。则是亦莫非天理之自然。如天但以雨露为教而无风霜。则不足为造化而成物之功息矣。故曰风雨霜露无非教。今岂可以风霜为非天地之教而又岂可谓涉乎人为也。戒慎恐惧。不须说太重者。盖言此心操则便存。只此便是本体。若著力把持。便是助长之病。盖此四字。说得重叠。学者恐有错认之弊。故发此义。此正为由教入之学者而设。非就圣人分上说也。末段读书之法。足以破世儒因袭之失。然窃恐人之为学。其不及者容有可至之时。而过去者未有回头之期。若不以圣言经训为准则而别用其心于新奇创开之论。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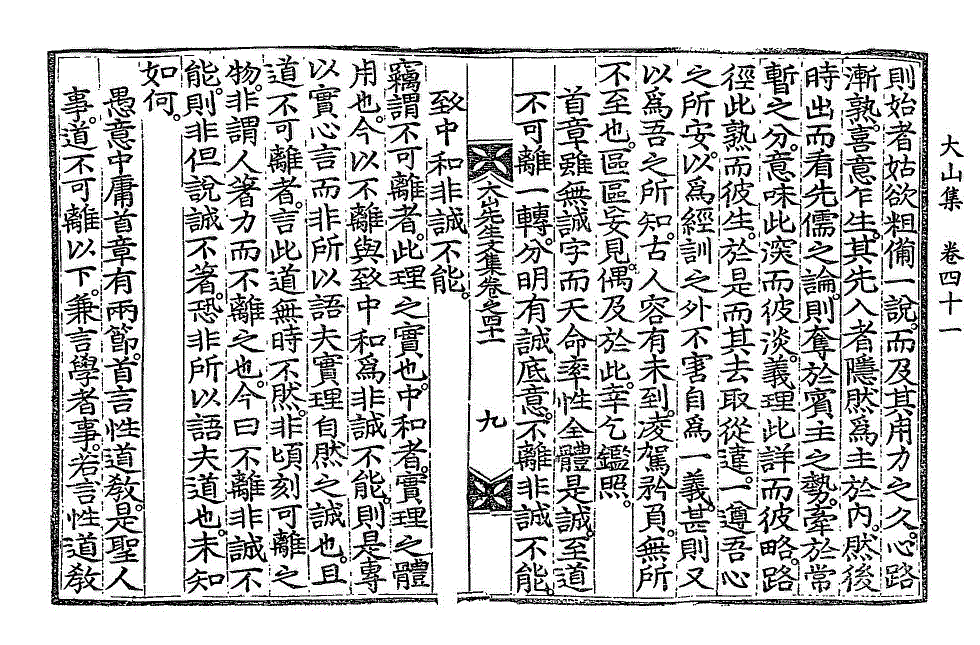 则始者姑欲粗备一说。而及其用力之久。心路渐熟。喜意乍生。其先入者隐然为主于内。然后时出而看先儒之论。则夺于宾主之势。牵于常暂之分。意味此深而彼淡。义理此详而彼略。路径此熟而彼生。于是而其去取从违。一遵吾心之所安。以为经训之外不害自为一义。甚则又以为吾之所知。古人容有未到。凌驾矜负。无所不至也。区区妄见。偶及于此。幸乞鉴照。
则始者姑欲粗备一说。而及其用力之久。心路渐熟。喜意乍生。其先入者隐然为主于内。然后时出而看先儒之论。则夺于宾主之势。牵于常暂之分。意味此深而彼淡。义理此详而彼略。路径此熟而彼生。于是而其去取从违。一遵吾心之所安。以为经训之外不害自为一义。甚则又以为吾之所知。古人容有未到。凌驾矜负。无所不至也。区区妄见。偶及于此。幸乞鉴照。首章虽无诚字而天命率性全体是诚。至道不可离一转。分明有诚底意。不离非诚不能。致中和非诚不能。
窃谓不可离者。此理之实也。中和者。实理之体用也。今以不离与致中和为非诚不能。则是专以实心言而非所以语夫实理自然之诚也。且道不可离者。言此道无时不然。非顷刻可离之物。非谓人著力而不离之也。今曰不离非诚不能。则非但说诚不著。恐非所以语夫道也。未知如何。
愚意中庸首章有两节。首言性道教。是圣人事。道不可离以下。兼言学者事。若言性道教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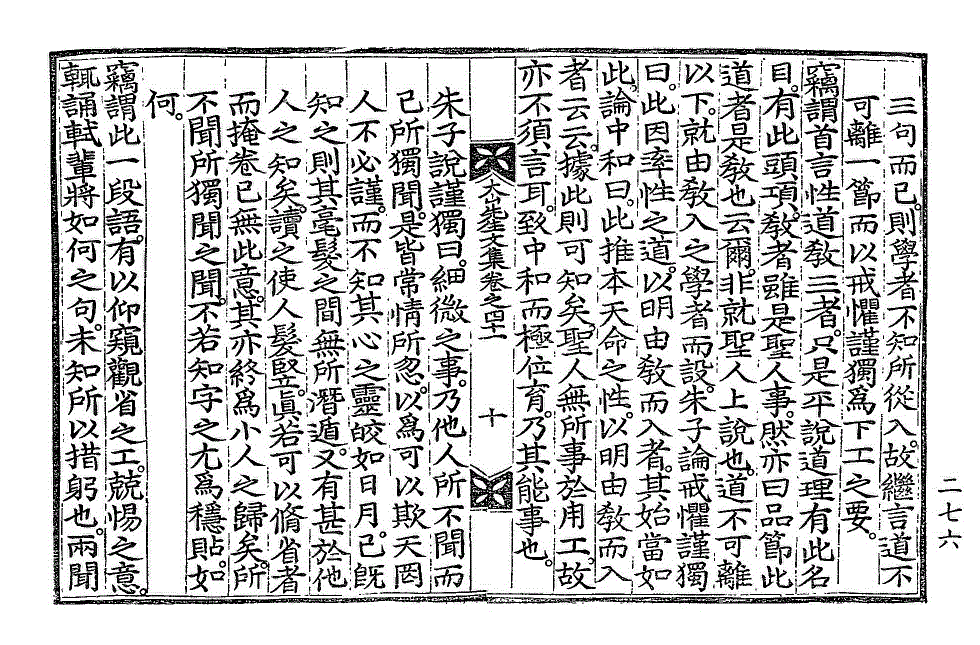 三句而已。则学者不知所从入。故继言道不可离一节而以戒惧谨独为下工之要。
三句而已。则学者不知所从入。故继言道不可离一节而以戒惧谨独为下工之要。窃谓首言性道教三者。只是平说道理有此名目。有此头项。教者虽是圣人事。然亦曰品节此道者是教也云尔。非就圣人上说也。道不可离以下。就由教入之学者而设。朱子论戒惧谨独曰。此因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当如此。论中和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云云。据此则可知矣。圣人无所事于用工。故亦不须言耳。致中和而极位育。乃其能事也。
朱子说谨独曰。细微之事。乃他人所不闻而己所独闻。是皆常情所忽。以为可以欺天罔人不必谨。而不知其心之灵皎如日月。己既知之则其毫发之间无所潜遁。又有甚于他人之知矣。读之使人发竖。真若可以脩省者而掩卷已无此意。其亦终为小人之归矣。所不闻所独闻之闻。不若知字之尤为稳贴。如何。
窃谓此一段语。有以仰窥观省之工。兢惕之意。辄诵轼辈将如何之句。未知所以措躬也。两闻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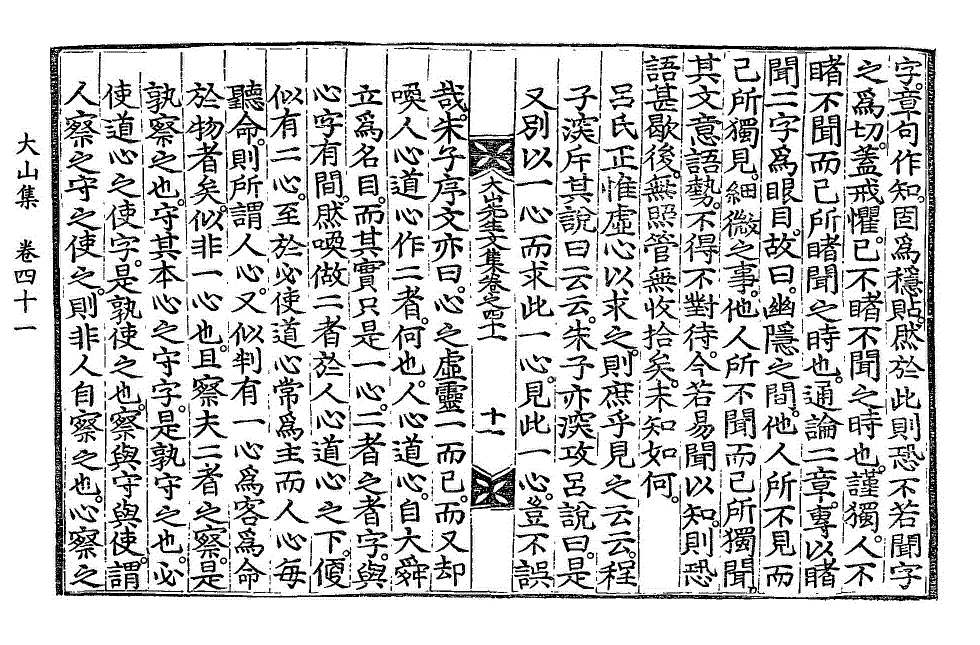 字。章句作知。固为稳贴。然于此则恐不若闻字之为切。盖戒惧。己不睹不闻之时也。谨独。人不睹不闻而己所睹闻之时也。通论二章。专以睹闻二字为眼目。故曰。幽隐之间。他人所不见而己所独见。细微之事。他人所不闻而己所独闻。其文意语势。不得不对待。今若易闻以知。则恐语甚歇后。无照管无收拾矣。未知如何。
字。章句作知。固为稳贴。然于此则恐不若闻字之为切。盖戒惧。己不睹不闻之时也。谨独。人不睹不闻而己所睹闻之时也。通论二章。专以睹闻二字为眼目。故曰。幽隐之间。他人所不见而己所独见。细微之事。他人所不闻而己所独闻。其文意语势。不得不对待。今若易闻以知。则恐语甚歇后。无照管无收拾矣。未知如何。吕氏正惟虚心以求之。则庶乎见之云云。程子深斥其说曰云云。朱子亦深攻吕说曰。是又别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见此一心。岂不误哉。朱子序文亦曰。心之虚灵一而已。而又却唤人心道心作二者。何也。人心道心。自大舜立为名目。而其实只是一心。二者之者字。与心字有间。然唤做二者于人心道心之下。便似有二心。至于必使道心常为主而人心每听命。则所谓人心。又似判有一心为客为命于物者矣。似非一心也。且察夫二者之察。是孰察之也。守其本心之守字。是孰守之也。必使道心之使字。是孰使之也。察与守与使。谓人察之守之使之。则非人自察之也。心察之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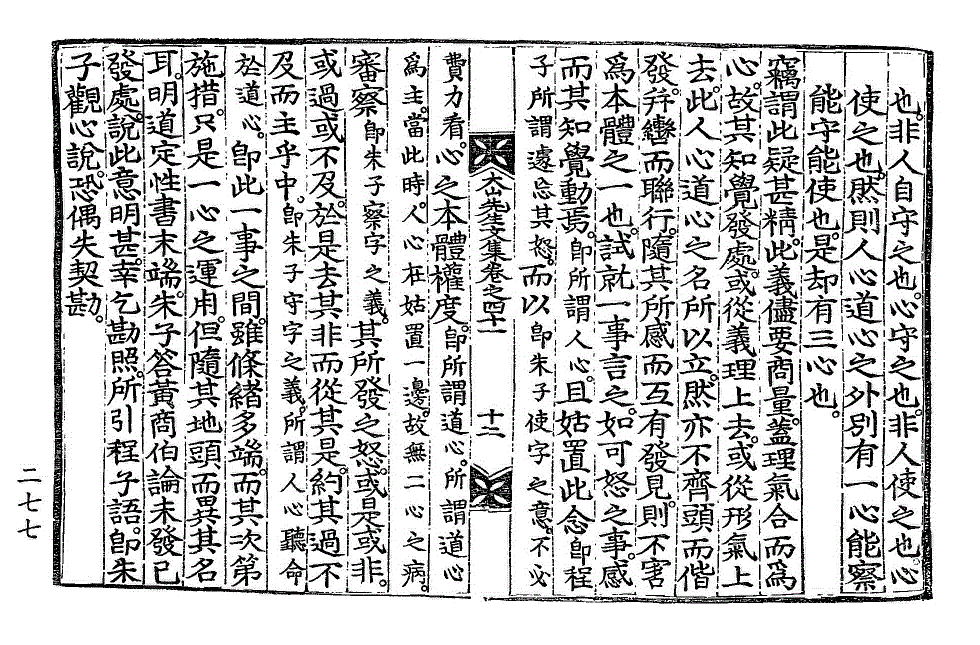 也。非人自守之也。心守之也。非人使之也。心使之也。然则人心道心之外别有一心能察能守能使也。是却有三心也。
也。非人自守之也。心守之也。非人使之也。心使之也。然则人心道心之外别有一心能察能守能使也。是却有三心也。窃谓此疑甚精。此义尽要商量。盖理气合而为心。故其知觉发处。或从义理上去。或从形气上去。此人心道心之名所以立。然亦不齐头而偕发。并辔而联行。随其所感而互有发见。则不害为本体之一也。试就一事言之。如可怒之事。感而其知觉动焉。(即所谓人心。)且姑置此念(即程子所谓遽忘其怒)而以(即朱子使字之意。不必费力看。)心之本体权度。(即所谓道心。所谓道心为主。当此时。人心在姑置一边。故无二心之病。)审察(即朱子察字之义)其所发之怒。或是或非。或过或不及。于是去其非而从其是。约其过不及而主乎中。(即朱子守字之义。所谓人心听命于道心。)即此一事之间。虽条绪多端。而其次第施措。只是一心之运用。但随其地头而异其名耳。明道定性书末端。朱子答黄商伯论未发已发处。说此意明甚。幸乞勘照。所引程子语。即朱子观心说。恐偶失契勘。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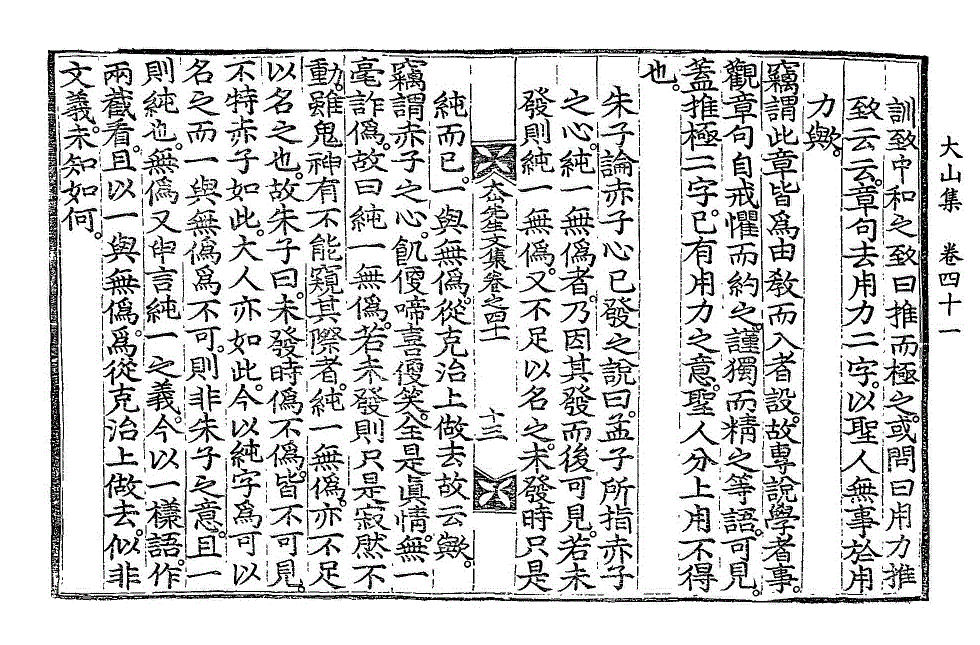 训致中和之致曰推而极之。或问曰用力推致云云。章句去用力二字。以圣人无事于用力欤。
训致中和之致曰推而极之。或问曰用力推致云云。章句去用力二字。以圣人无事于用力欤。窃谓此章皆为由教而入者设。故专说学者事。观章句自戒惧而约之。谨独而精之等语。可见。盖推极二字。已有用力之意。圣人分上用不得也。
朱子论赤子心已发之说曰。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者。乃因其发而后可见。若未发则纯一无伪。又不足以名之。未发时只是纯而已。一与无伪。从克治上做去故云欤。
窃谓赤子之心。饥便啼喜便笑。全是真情。无一毫诈伪。故曰纯一无伪。若未发则只是寂然不动。虽鬼神有不能窥其际者。纯一无伪。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朱子曰。未发时伪不伪。皆不可见。不特赤子如此。大人亦如此。今以纯字为可以名之而一与无伪为不可。则非朱子之意。且一则纯也。无伪又申言纯一之义。今以一样语。作两截看。且以一与无伪。为从克治上做去。似非文义。未知如何。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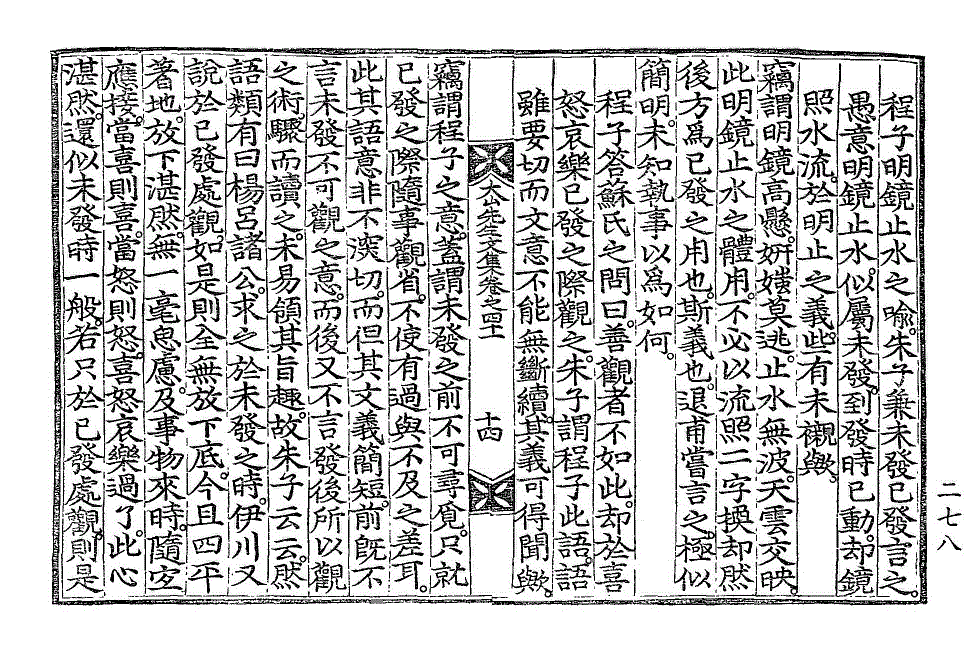 程子明镜止水之喻。朱子兼未发已发言之。愚意明镜止水。似属未发。到发时已动。却镜照水流。于明止之义。些有未衬欤。
程子明镜止水之喻。朱子兼未发已发言之。愚意明镜止水。似属未发。到发时已动。却镜照水流。于明止之义。些有未衬欤。窃谓明镜高悬。妍媸莫逃。止水无波。天云交映。此明镜止水之体用。不必以流照二字换却然后方为已发之用也。斯义也。退甫尝言之。极似简明。未知执事以为如何。
程子答苏氏之问曰。善观者不如此。却于喜怒哀乐已发之际观之。朱子谓程子此语。语虽要切而文意不能无断续。其义可得闻欤。
窃谓程子之意。盖谓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只就已发之际随事观省。不使有过与不及之差耳。此其语意非不深切。而但其文义简短。前既不言未发不可观之意。而后又不言发后所以观之术。骤而读之。未易领其旨趣。故朱子云云。然语类有曰杨吕诸公。求之于未发之时。伊川又说于已发处观。如是则全无放下底。今且四平著地。放下湛然。无一毫思虑。及事物来时。随宜应接。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喜怒哀乐过了。此心湛然。还似未发时一般。若只于已发处观。则是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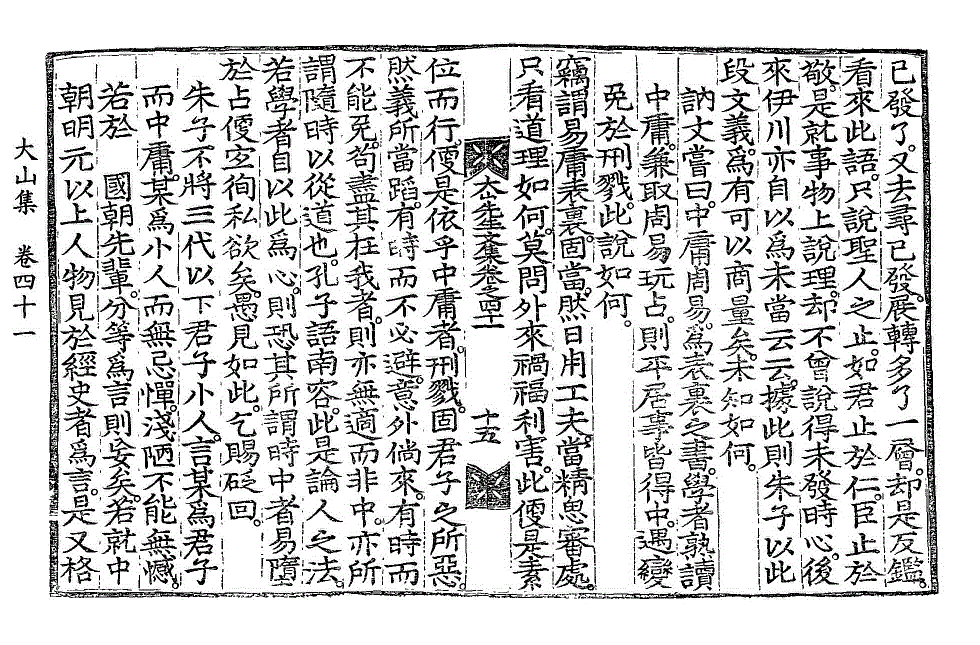 已发了。又去寻已发。展转多了一层。却是反鉴。看来此语。只说圣人之止。如君止于仁。臣止于敬。是就事物上说理。却不曾说得未发时心。后来伊川亦自以为未当云云。据此则朱子以此段文义。为有可以商量矣。未知如何。
已发了。又去寻已发。展转多了一层。却是反鉴。看来此语。只说圣人之止。如君止于仁。臣止于敬。是就事物上说理。却不曾说得未发时心。后来伊川亦自以为未当云云。据此则朱子以此段文义。为有可以商量矣。未知如何。讷丈尝曰。中庸周易。为表里之书。学者熟读中庸。兼取周易玩占。则平居事皆得中。遇变免于刑戮。此说如何。
窃谓易庸表里。固当。然日用工夫。当精思审处。只看道理如何。莫问外来祸福利害。此便是素位而行。便是依乎中庸者。刑戮。固君子之所恶。然义所当蹈。有时而不必避。意外倘来。有时而不能免。苟尽其在我者。则亦无适而非中。亦所谓随时以从道也。孔子语南容。此是论人之法。若学者自以此为心。则恐其所谓时中者易堕于占便宜徇私欲矣。愚见如此。乞赐砭回。
朱子不将三代以下君子小人。言某为君子而中庸。某为小人而无忌惮。浅陋不能无憾。若于 国朝先辈。分等为言则妄矣。若就中朝明元以上人物见于经史者为言。是又格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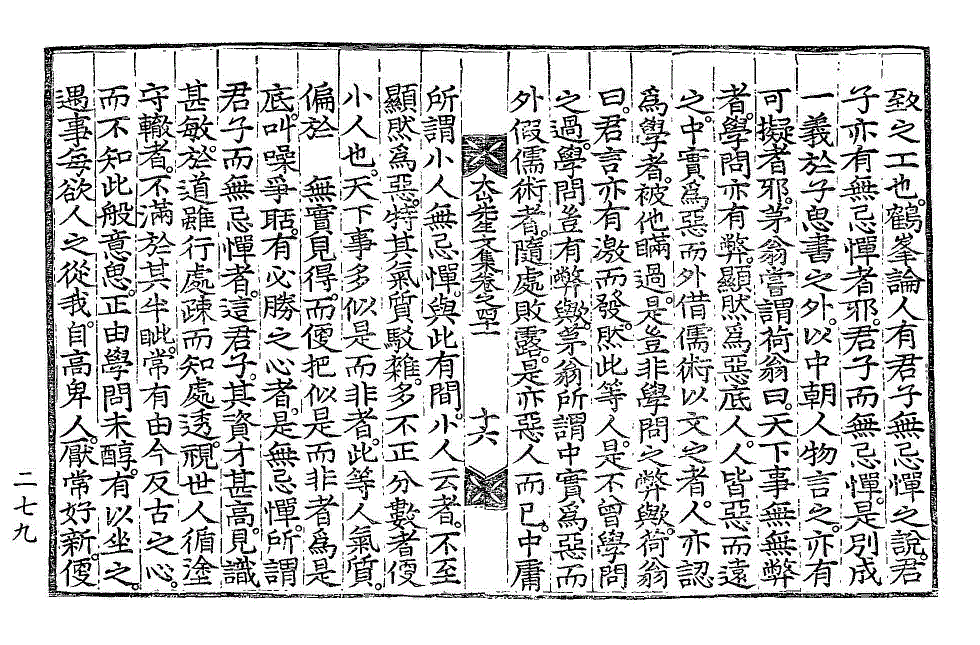 致之工也。鹤峰论人有君子无忌惮之说。君子亦有无忌惮者邪。君子而无忌惮。是别成一义于子思书之外。以中朝人物言之。亦有可拟者邪。茅翁尝谓荷翁曰。天下事无无弊者。学问亦有弊。显然为恶底人。人皆恶而远之。中实为恶而外借儒术以文之者。人亦认为学者。被他瞒过。是岂非学问之弊欤。荷翁曰。君言亦有激而发。然此等人。是不曾学问之过。学问岂有弊欤。茅翁所谓中实为恶而外假儒术者。随处败露。是亦恶人而已。中庸所谓小人无忌惮。与此有间。小人云者。不至显然为恶。特其气质驳杂。多不正分数者便小人也。天下事多似是而非者。此等人气质。偏于 无实见得。而便把似是而非者为是底。叫噪争聒。有必胜之心者。是无忌惮。所谓君子而无忌惮者。这君子。其资才甚高。见识甚敏。于道虽行处疏而知处透。视世人循涂守辙者。不满于其半眦。常有由今反古之心。而不知此般意思。正由学问未醇。有以坐之。遇事每欲人之从我。自高卑人。厌常好新。便
致之工也。鹤峰论人有君子无忌惮之说。君子亦有无忌惮者邪。君子而无忌惮。是别成一义于子思书之外。以中朝人物言之。亦有可拟者邪。茅翁尝谓荷翁曰。天下事无无弊者。学问亦有弊。显然为恶底人。人皆恶而远之。中实为恶而外借儒术以文之者。人亦认为学者。被他瞒过。是岂非学问之弊欤。荷翁曰。君言亦有激而发。然此等人。是不曾学问之过。学问岂有弊欤。茅翁所谓中实为恶而外假儒术者。随处败露。是亦恶人而已。中庸所谓小人无忌惮。与此有间。小人云者。不至显然为恶。特其气质驳杂。多不正分数者便小人也。天下事多似是而非者。此等人气质。偏于 无实见得。而便把似是而非者为是底。叫噪争聒。有必胜之心者。是无忌惮。所谓君子而无忌惮者。这君子。其资才甚高。见识甚敏。于道虽行处疏而知处透。视世人循涂守辙者。不满于其半眦。常有由今反古之心。而不知此般意思。正由学问未醇。有以坐之。遇事每欲人之从我。自高卑人。厌常好新。便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0H 页
 是无忌惮邪。以弊端言之。小人之无忌惮。其弊反小。君子而无忌惮。其弊有不可胜言。以上文朱子说断之。此君子是君子而处不得中者欤。以心学言之。其去小人。才一间欤。
是无忌惮邪。以弊端言之。小人之无忌惮。其弊反小。君子而无忌惮。其弊有不可胜言。以上文朱子说断之。此君子是君子而处不得中者欤。以心学言之。其去小人。才一间欤。窃谓小人之无忌惮者。盖其用心不正。与君子之有德者不同而行己恣肆。又与君子之戒惧者相反。今以驳杂不正分数为小人。则与章句所谓有小人之心者不合。以似是而非者为是而有必胜之心者为无忌惮。则与章句所谓肆欲妄行者不同矣。盖君子小人。其设心有善恶之殊。故其制行有敬肆之分。恐不可如是罪重而罚轻也。金先生君子无忌惮一转语。未及承见。不敢臆为之说。弊端大小。固如所论。然亦当原情定罪。不可一例勘断。去小人才一间。恐亦非君子恕人之论。盖不可以本心之无他而不责其贻弊之罪。然亦不可以为弊之大而不究其本情之故失。恐于此平心舒究。不使相掩。方是君子论人之法。若君子以之自治。则其心法之严。不得不如来谕之云耳。荷翁所以语茅山者。辞简而义严。温乎有德之言也。诵而味之。不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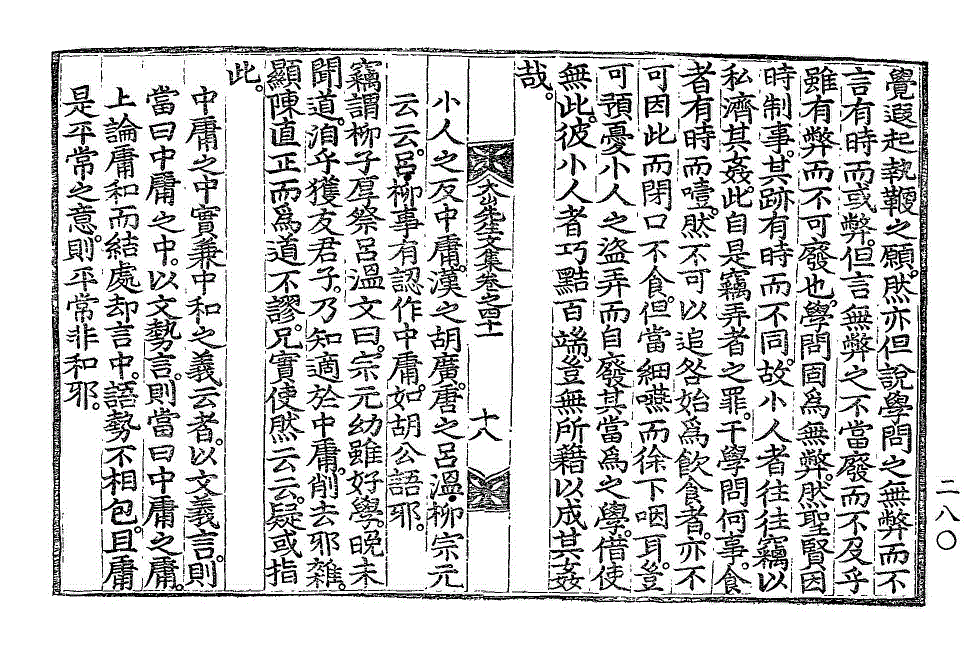 觉遐起执鞭之愿。然亦但说学问之无弊而不言有时而或弊。但言无弊之不当废而不及乎虽有弊而不可废也。学问固为无弊。然圣贤因时制事。其迹有时而不同。故小人者往往窃以私济其奸。此自是窃弄者之罪。干学问何事。食者有时而噎。然不可以追咎始为饮食者。亦不可因此而闭口不食。但当细咽而徐下咽耳。岂可预忧小人之盗弄而自废其当为之学。借使无此。彼小人者巧黠百端。岂无所藉以成其奸哉。
觉遐起执鞭之愿。然亦但说学问之无弊而不言有时而或弊。但言无弊之不当废而不及乎虽有弊而不可废也。学问固为无弊。然圣贤因时制事。其迹有时而不同。故小人者往往窃以私济其奸。此自是窃弄者之罪。干学问何事。食者有时而噎。然不可以追咎始为饮食者。亦不可因此而闭口不食。但当细咽而徐下咽耳。岂可预忧小人之盗弄而自废其当为之学。借使无此。彼小人者巧黠百端。岂无所藉以成其奸哉。小人之反中庸。汉之胡广。唐之吕温,柳宗元云云。吕,柳事有认作中庸。如胡公语邪。
窃谓柳子厚祭吕温文曰。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云云。疑或指此。
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云者。以文义言。则当曰中庸之中。以文势言。则当曰中庸之庸。上论庸和而结处却言中。语势不相包。且庸是平常之意。则平常非和邪。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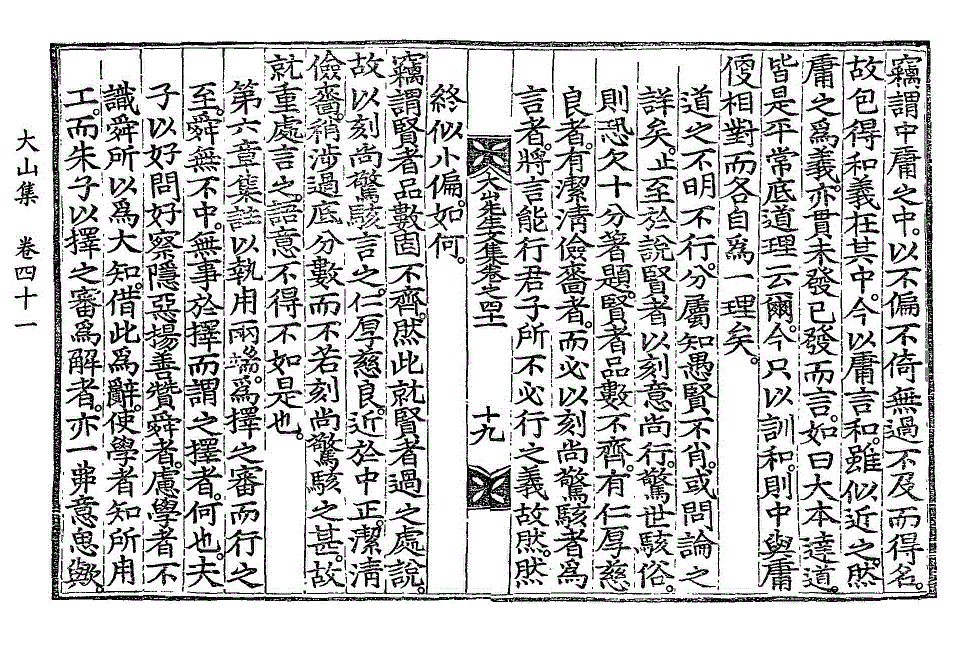 窃谓中庸之中。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得名。故包得和义在其中。今以庸言和。虽似近之。然庸之为义。亦贯未发已发而言。如曰大本达道。皆是平常底道理云尔。今只以训和。则中与庸便相对而各自为一理矣。
窃谓中庸之中。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得名。故包得和义在其中。今以庸言和。虽似近之。然庸之为义。亦贯未发已发而言。如曰大本达道。皆是平常底道理云尔。今只以训和。则中与庸便相对而各自为一理矣。道之不明不行。分属知愚贤不肖。或问论之详矣。(止)至于说贤者以刻意尚行。惊世骇俗。则恐欠十分著题。贤者品数不齐。有仁厚慈良者。有洁清俭啬者。而必以刻尚惊骇者为言者。将言能行君子所不必行之义故然。然终似小偏。如何。
窃谓贤者品数固不齐。然此就贤者过之处说。故以刻尚惊骇言之。仁厚慈良。近于中正。洁清俭啬。稍涉过底分数而不若刻尚惊骇之甚。故就重处言之。语意不得不如是也。
第六章集注以执用两端。为择之审而行之至。舜无不中。无事于择而谓之择者。何也。夫子以好问好察隐恶扬善赞舜者。虑学者不识舜所以为大知。借此为辞。使学者知所用工。而朱子以择之审为解者。亦一串意思欤。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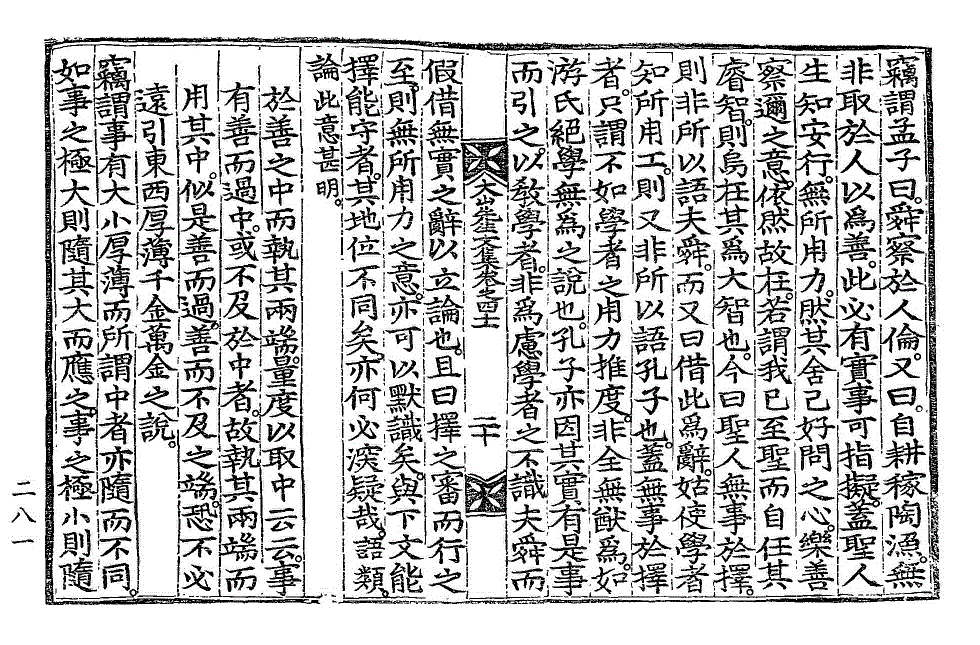 窃谓孟子曰。舜察于人伦。又曰。自耕稼陶渔。无非取于人以为善。此必有实事可指拟。盖圣人生知安行。无所用力。然其舍己好问之心。乐善察迩之意。依然故在。若谓我已至圣而自任其睿智。则乌在其为大智也。今曰圣人无事于择。则非所以语夫舜。而又曰借此为辞。姑使学者知所用工。则又非所以语孔子也。盖无事于择者。只谓不如学者之用力推度。非全无猷为。如游氏绝学无为之说也。孔子亦因其实有是事而引之。以教学者。非为虑学者之不识夫舜而假借无实之辞以立论也。且曰择之审而行之至。则无所用力之意。亦可以默识矣。与下文能择能守者。其地位不同矣。亦何必深疑哉。(语类。论此意甚明。)
窃谓孟子曰。舜察于人伦。又曰。自耕稼陶渔。无非取于人以为善。此必有实事可指拟。盖圣人生知安行。无所用力。然其舍己好问之心。乐善察迩之意。依然故在。若谓我已至圣而自任其睿智。则乌在其为大智也。今曰圣人无事于择。则非所以语夫舜。而又曰借此为辞。姑使学者知所用工。则又非所以语孔子也。盖无事于择者。只谓不如学者之用力推度。非全无猷为。如游氏绝学无为之说也。孔子亦因其实有是事而引之。以教学者。非为虑学者之不识夫舜而假借无实之辞以立论也。且曰择之审而行之至。则无所用力之意。亦可以默识矣。与下文能择能守者。其地位不同矣。亦何必深疑哉。(语类。论此意甚明。)于善之中而执其两端。量度以取中云云。事有善而过中。或不及于中者。故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似是善而过。善而不及之端。恐不必远引东西厚薄千金万金之说。
窃谓事有大小厚薄而所谓中者亦随而不同。如事之极大则随其大而应之。事之极小则随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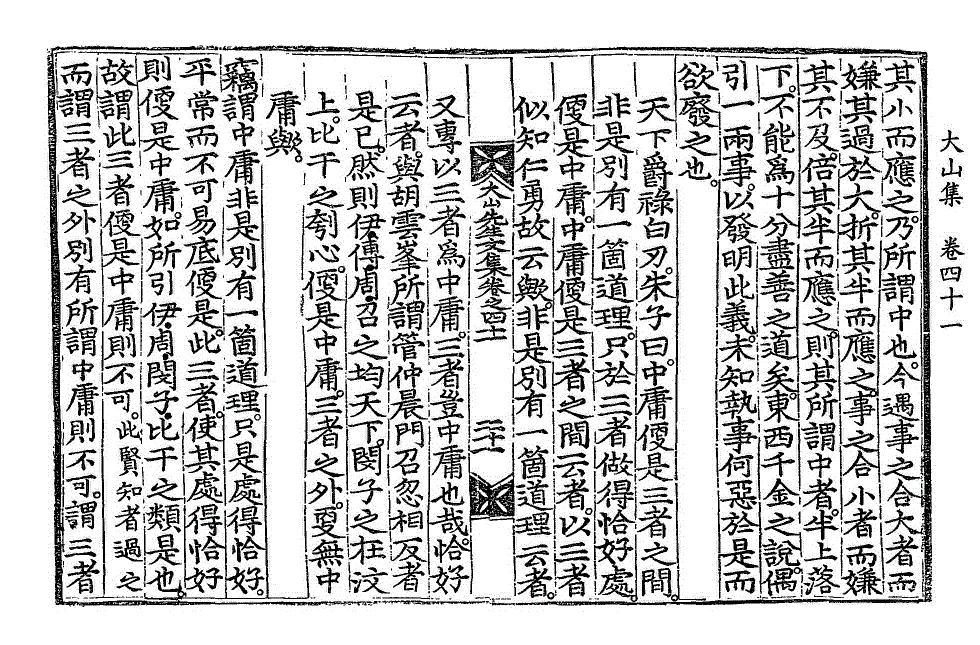 其小而应之。乃所谓中也。今遇事之合大者而嫌其过于大。折其半而应之。事之合小者而嫌其不及。倍其半而应之。则其所谓中者。半上落下。不能为十分尽善之道矣。东西千金之说。偶引一两事。以发明此义。未知执事何恶于是而欲废之也。
其小而应之。乃所谓中也。今遇事之合大者而嫌其过于大。折其半而应之。事之合小者而嫌其不及。倍其半而应之。则其所谓中者。半上落下。不能为十分尽善之道矣。东西千金之说。偶引一两事。以发明此义。未知执事何恶于是而欲废之也。天下爵禄白刃。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间。非是别有一个道理。只于三者做得恰好处。便是中庸。中庸便是三者之间云者。以三者似知仁勇故云欤。非是别有一个道理云者。又专以三者为中庸。三者岂中庸也哉。恰好云者。与胡云峰所谓管仲晨门召忽相反者是已。然则伊,傅,周,召之均天下。闵子之在汶上。比干之刳心。便是中庸。三者之外。更无中庸欤。
窃谓中庸非是别有一个道理。只是处得恰好。平常而不可易底便是。此三者。使其处得恰好则便是中庸。如所引伊,周,闵子,比干之类是也。故谓此三者便是中庸则不可。(此贤知者过之。)而谓三者之外别有所谓中庸则不可。谓三者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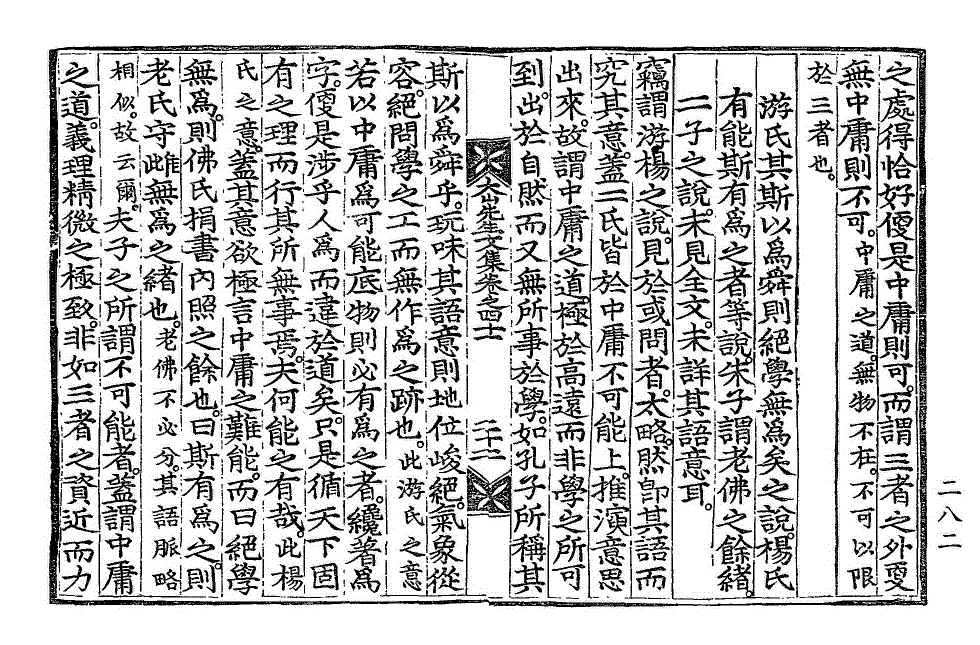 之处得恰好便是中庸则可。而谓三者之外更无中庸则不可。(中庸之道。无物不在。不可以限于三者也。)
之处得恰好便是中庸则可。而谓三者之外更无中庸则不可。(中庸之道。无物不在。不可以限于三者也。)游氏其斯以为舜则绝学无为矣之说。杨氏有能斯有为之者等说。朱子谓老佛之馀绪。二子之说。未见全文。未详其语意耳。
窃谓游,杨之说。见于或问者。太略。然即其语而究其意。盖二氏皆于中庸不可能上。推演意思出来。故谓中庸之道。极于高远而非学之所可到。出于自然而又无所事于学。如孔子所称其斯以为舜乎。玩味其语意则地位峻绝。气象从容。绝问学之工而无作为之迹也。(此游氏之意。)若以中庸为可能底物则必有为之者。才著为字。便是涉乎人为而违于道矣。只是循天下固有之理而行其所无事焉。夫何能之有哉。(此杨氏之意。)盖其意欲极言中庸之难能。而曰绝学无为。则佛氏捐书内照之馀也。曰斯有为之。则老氏守雌无为之绪也。(老佛不必分。其语脉略相似。故云尔。)夫子之所谓不可能者。盖谓中庸之道。义理精微之极致。非如三者之资近而力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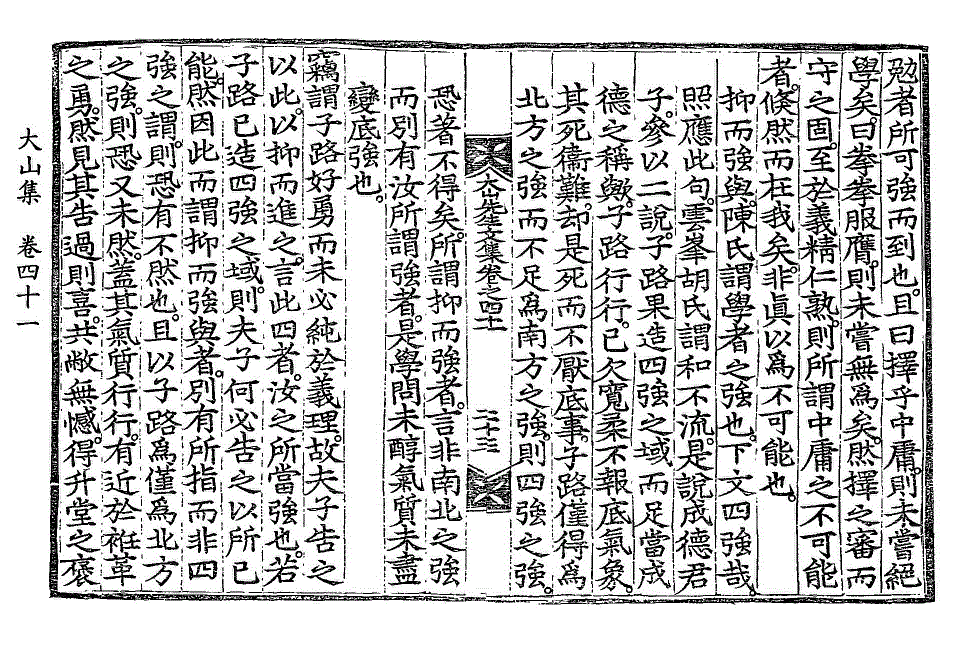 勉者所可强而到也。且曰择乎中庸。则未尝绝学矣。曰拳拳服膺。则未尝无为矣。然择之审而守之固。至于义精仁熟。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倏然而在我矣。非真以为不可能也。
勉者所可强而到也。且曰择乎中庸。则未尝绝学矣。曰拳拳服膺。则未尝无为矣。然择之审而守之固。至于义精仁熟。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倏然而在我矣。非真以为不可能也。抑而强与。陈氏谓学者之强也。下文四强哉。照应此句。云峰胡氏谓和不流。是说成德君子。参以二说。子路果造四强之域而足当成德之称欤。子路行行。已欠宽柔不报底气象。其死卫难。却是死而不厌底事。子路仅得为北方之强而不足为南方之强。则四强之强。恐著不得矣。所谓抑而强者。言非南北之强而别有汝所谓强者。是学问未醇气质未尽变底强也。
窃谓子路好勇而未必纯于义理。故夫子告之以此。以抑而进之。言此四者。汝之所当强也。若子路已造四强之域。则夫子何必告之以所已能。然因此而谓抑而强与者。别有所指而非四强之谓。则恐有不然也。且以子路为仅为北方之强。则恐又未然。盖其气质行行。有近于衽革之勇。然见其告过则喜。共敝无憾。得升堂之褒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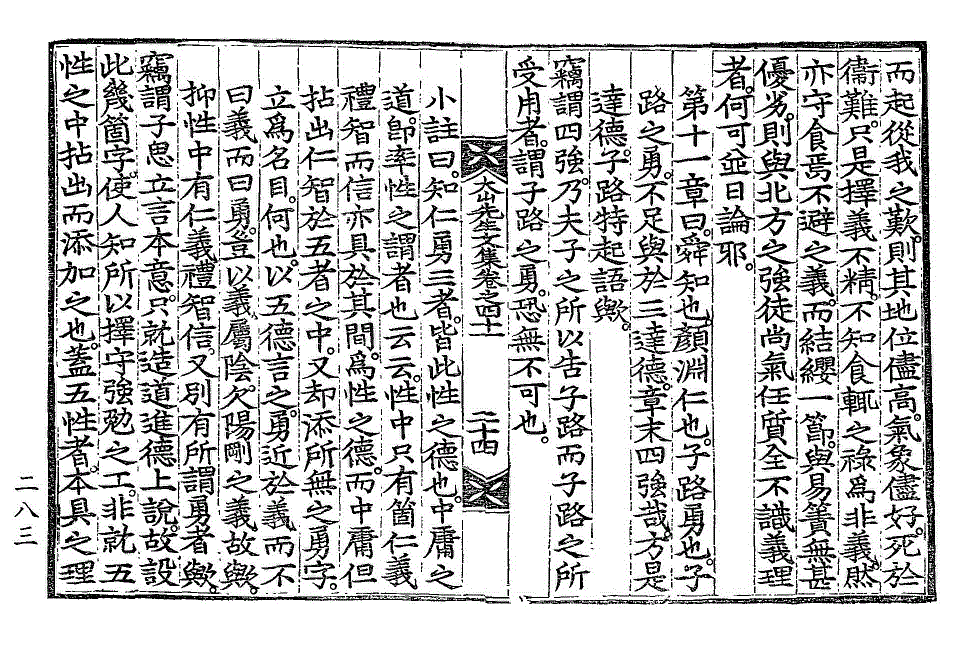 而起从我之叹。则其地位尽高。气象尽好。死于卫难。只是择义不精。不知食辄之禄为非义。然亦守食焉不避之义。而结缨一节。与易箦无甚优劣。则与北方之强徒尚气任质全不识义理者。何可并日论邪。
而起从我之叹。则其地位尽高。气象尽好。死于卫难。只是择义不精。不知食辄之禄为非义。然亦守食焉不避之义。而结缨一节。与易箦无甚优劣。则与北方之强徒尚气任质全不识义理者。何可并日论邪。第十一章曰。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子路之勇。不足与于三达德。章末四强哉。方是达德。子路特起语欤。
窃谓四强。乃夫子之所以告子路而子路之所受用者。谓子路之勇。恐无不可也。
小注曰。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谓者也云云。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而信亦具于其间。为性之德。而中庸但拈出仁智于五者之中。又却添所无之勇字。立为名目。何也。以五德言之。勇近于义而不曰义而曰勇。岂以义属阴。欠阳刚之义故欤。抑性中有仁义礼智信。又别有所谓勇者欤。
窃谓子思立言本意。只就造道进德上说。故设此几个字。使人知所以择守强勉之工。非就五性之中拈出而添加之也。盖五性者。本具之理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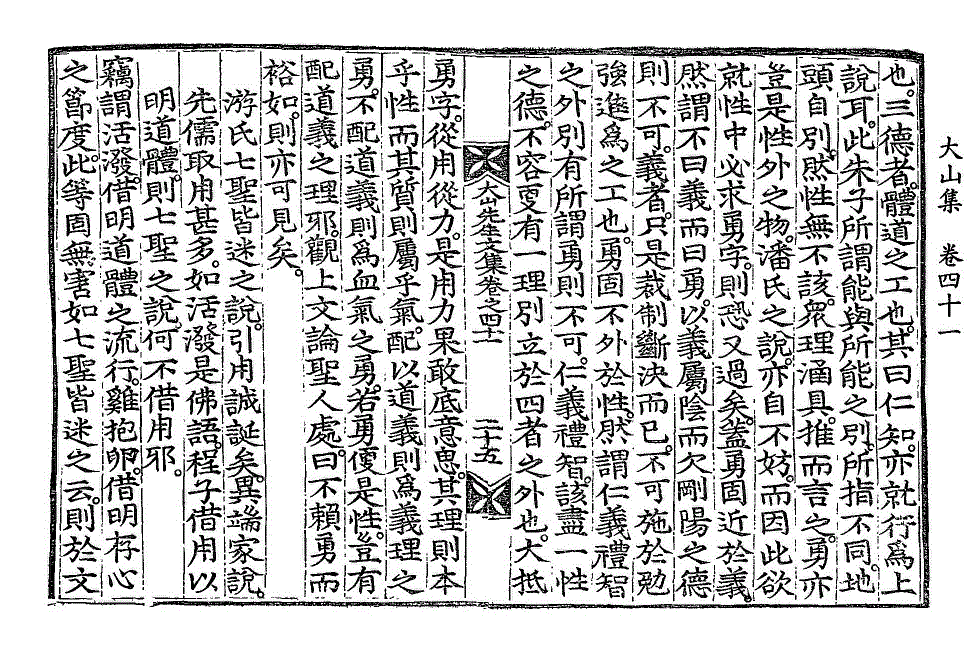 也。三德者。体道之工也。其曰仁知。亦就行为上说耳。此朱子所谓能与所能之别。所指不同。地头自别。然性无不该。众理涵具。推而言之。勇亦岂是性外之物。潘氏之说。亦自不妨。而因此欲就性中必求勇字。则恐又过矣。盖勇固近于义。然谓不曰义而曰勇。以义属阴而欠刚阳之德则不可。义者。只是裁制断决而已。不可施于勉强进为之工也。勇固不外于性。然谓仁义礼智之外别有所谓勇则不可。仁义礼智。该尽一性之德。不容更有一理别立于四者之外也。大抵勇字。从用从力。是用力果敢底意思。其理则本乎性而其质则属乎气。配以道义则为义理之勇。不配道义则为血气之勇。若勇便是性。岂有配道义之理邪。观上文论圣人处。曰不赖勇而裕如。则亦可见矣。
也。三德者。体道之工也。其曰仁知。亦就行为上说耳。此朱子所谓能与所能之别。所指不同。地头自别。然性无不该。众理涵具。推而言之。勇亦岂是性外之物。潘氏之说。亦自不妨。而因此欲就性中必求勇字。则恐又过矣。盖勇固近于义。然谓不曰义而曰勇。以义属阴而欠刚阳之德则不可。义者。只是裁制断决而已。不可施于勉强进为之工也。勇固不外于性。然谓仁义礼智之外别有所谓勇则不可。仁义礼智。该尽一性之德。不容更有一理别立于四者之外也。大抵勇字。从用从力。是用力果敢底意思。其理则本乎性而其质则属乎气。配以道义则为义理之勇。不配道义则为血气之勇。若勇便是性。岂有配道义之理邪。观上文论圣人处。曰不赖勇而裕如。则亦可见矣。游氏七圣皆迷之说。引用诚诞矣。异端家说。先儒取用甚多。如活泼是佛语。程子借用以明道体。则七圣之说。何不借用邪。
窃谓活泼。借明道体之流行。鸡抱卵。借明存心之节度。此等固无害如七圣皆迷之云。则于文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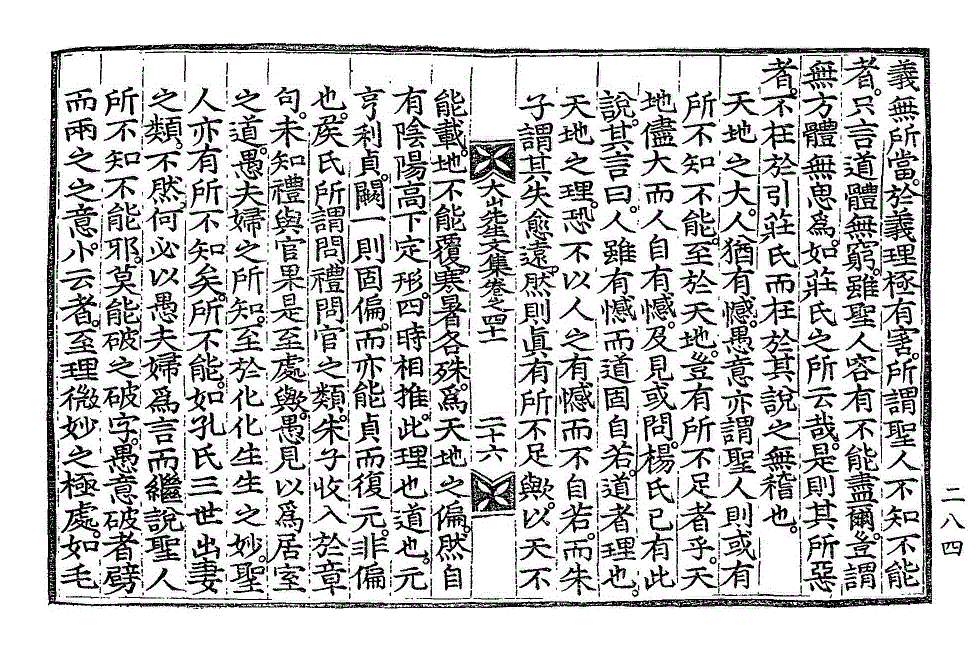 义无所当。于义理极有害。所谓圣人不知不能者。只言道体无穷。虽圣人容有不能尽尔。岂谓无方体无思为。如庄氏之所云哉。是则其所恶者。不在于引庄氏而在于其说之无稽也。
义无所当。于义理极有害。所谓圣人不知不能者。只言道体无穷。虽圣人容有不能尽尔。岂谓无方体无思为。如庄氏之所云哉。是则其所恶者。不在于引庄氏而在于其说之无稽也。天地之大。人犹有憾。愚意亦谓圣人则或有所不知不能。至于天地。岂有所不足者乎。天地尽大而人自有憾。及见或问。杨氏已有此说。其言曰。人虽有憾而道固自若。道者理也。天地之理。恐不以人之有憾而不自若。而朱子谓其失愈远。然则真有所不足欤。以天不能载。地不能覆。寒暑各殊。为天地之偏。然自有阴阳高下定形。四时相推。此理也道也。元亨利贞。阙一则固偏。而亦能贞而复元。非偏也。侯氏所谓问礼问官之类。朱子收入于章句。未知礼与官果是至处欤。愚见以为居室之道。愚夫妇之所知。至于化化生生之妙。圣人亦有所不知矣。所不能。如孔氏三世出妻之类。不然。何必以愚夫妇为言而继说圣人所不知不能邪。莫能破之破字。愚意破者劈而两之之意。小云者。至理微妙之极处。如毛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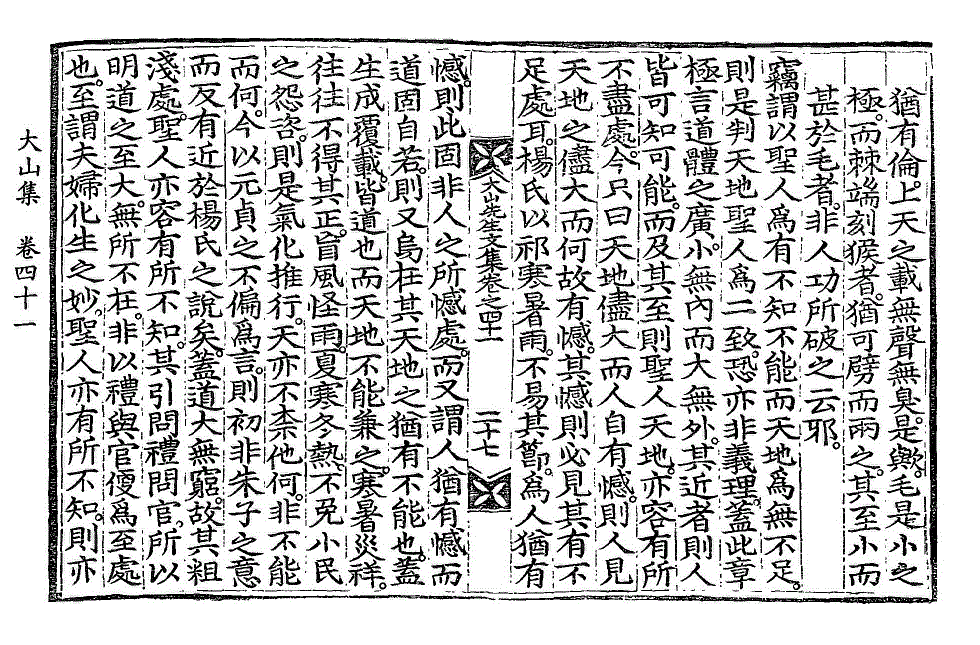 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是欤。毛是小之极。而棘端刻猴者。犹可劈而两之。其至小而甚于毛者。非人功所破之云邪。
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是欤。毛是小之极。而棘端刻猴者。犹可劈而两之。其至小而甚于毛者。非人功所破之云邪。窃谓以圣人为有不知不能而天地为无不足。则是判天地圣人为二致。恐亦非义理。盖此章极言道体之广。小无内而大无外。其近者则人皆可知可能。而及其至则圣人天地。亦容有所不尽处。今只曰天地尽大而人自有憾。则人见天地之尽大而何故有憾。其憾则必见其有不足处耳。杨氏以祁寒暑雨。不易其节。为人犹有憾。则此固非人之所憾处。而又谓人犹有憾而道固自若。则又乌在其天地之犹有不能也。盖生成覆载。皆道也而天地不能兼之。寒暑灾祥。往往不得其正。盲风怪雨。夏寒冬热。不免小民之怨咨。则是气化推行。天亦不柰他何。非不能而何。今以元贞之不偏为言。则初非朱子之意而反有近于杨氏之说矣。盖道大无穷。故其粗浅处。圣人亦容有所不知。其引问礼问官。所以明道之至大。无所不在。非以礼与官便为至处也。至谓夫妇化生之妙。圣人亦有所不知。则亦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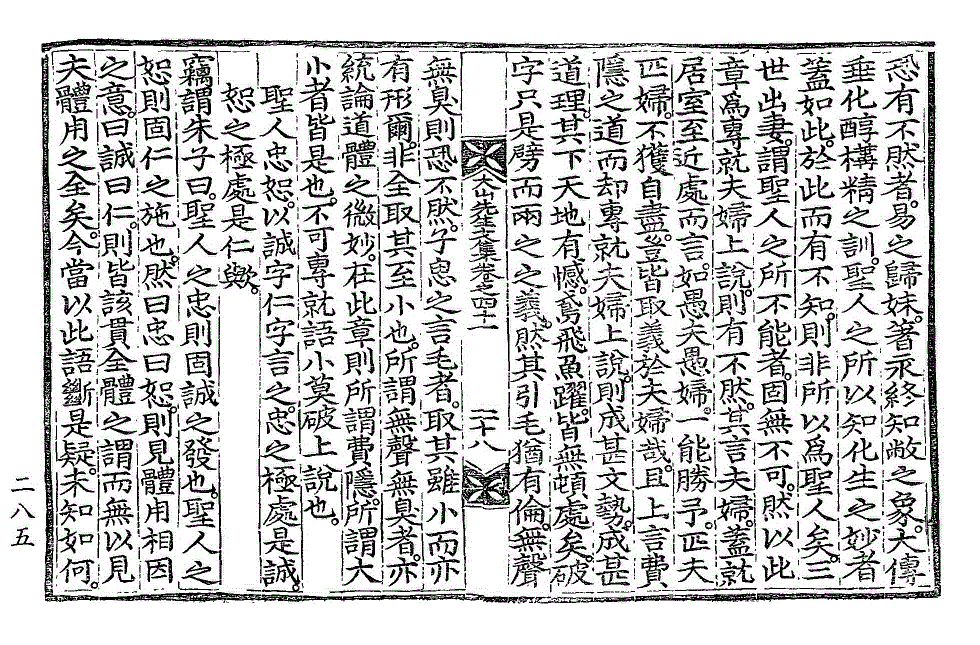 恐有不然者。易之归妹。著永终知敝之象。大传垂化醇构精之训。圣人之所以知化生之妙者盖如此。于此而有不知。则非所以为圣人矣。三世出妻。谓圣人之所不能者。固无不可。然以此章为专就夫妇上说。则有不然。其言夫妇。盖就居室至近处而言。如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匹夫匹妇。不获自尽。岂皆取义于夫妇哉。且上言费隐之道而却专就夫妇上说。则成甚文势。成甚道理。其下天地有憾。鸢飞鱼跃。皆无顿处矣。破字只是劈而两之之义。然其引毛犹有伦。无声无臭则恐不然。子思之言毛者。取其虽小而亦有形尔。非全取其至小也。所谓无声无臭者。亦统论道体之微妙。在此章则所谓费隐。所谓大小者皆是也。不可专就语小莫破上说也。
恐有不然者。易之归妹。著永终知敝之象。大传垂化醇构精之训。圣人之所以知化生之妙者盖如此。于此而有不知。则非所以为圣人矣。三世出妻。谓圣人之所不能者。固无不可。然以此章为专就夫妇上说。则有不然。其言夫妇。盖就居室至近处而言。如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匹夫匹妇。不获自尽。岂皆取义于夫妇哉。且上言费隐之道而却专就夫妇上说。则成甚文势。成甚道理。其下天地有憾。鸢飞鱼跃。皆无顿处矣。破字只是劈而两之之义。然其引毛犹有伦。无声无臭则恐不然。子思之言毛者。取其虽小而亦有形尔。非全取其至小也。所谓无声无臭者。亦统论道体之微妙。在此章则所谓费隐。所谓大小者皆是也。不可专就语小莫破上说也。圣人忠恕。以诚字仁字言之。忠之极处是诚。恕之极处是仁欤。
窃谓朱子曰。圣人之忠则固诚之发也。圣人之恕则固仁之施也。然曰忠曰恕。则见体用相因之意。曰诚曰仁。则皆该贯全体之谓而无以见夫体用之全矣。今当以此语断是疑。未知如何。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6H 页
 在上不陵。在下不援。愚意不援易。不陵难。不援。乡党自好者。或可以能之。若处隆赫之位。能不骄不陵。非素位君子。不能矣。
在上不陵。在下不援。愚意不援易。不陵难。不援。乡党自好者。或可以能之。若处隆赫之位。能不骄不陵。非素位君子。不能矣。窃谓此因所遇各异。本不当论优劣。然处富易而处贫难。顺境易而逆境难。乡党自好之不援。亦是平平可堪之事。若阨穷之甚。祸患之逼。转触捩覆。桎梏箠楚。则当此时。苟有攀援之势。能不引手开口者鲜矣。纵不太作形迹。心里泰然。全无恨憾之意否。此则又有甚于处富不陵者之事顺而势易。故程子曰。学者学处患难。富贵荣达。即不须学。亦此意也。
居易以俟命。是君子事。然所谓易是至不易。何如可以至于易邪。
窃谓患难贫富。即昼夜寒暑之道也。君子一夷险齐忧乐。故所处者皆平常而无艰险。然其所以至此则无他道焉。格致研究而极明理之工。祇慎畏惧而严持身之法。惩窒迁改之工。不懈于日用。修省动忍之方。益笃于造次。养气而配道义则足以无惧。乐道而忘势利则足以无求。经历之久则所存者益熟。操虑之深则所守者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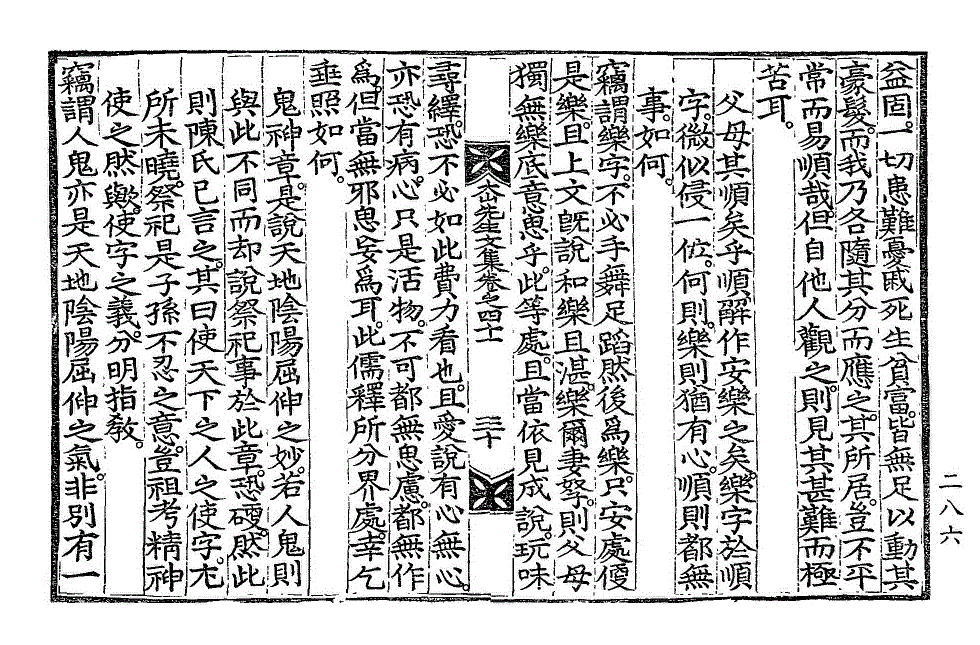 益固。一切患难忧戚死生贫富。皆无足以动其豪发。而我乃各随其分而应之。其所居。岂不平常而易顺哉。但自他人观之。则见其甚难而极苦耳。
益固。一切患难忧戚死生贫富。皆无足以动其豪发。而我乃各随其分而应之。其所居。岂不平常而易顺哉。但自他人观之。则见其甚难而极苦耳。父母其顺矣乎顺。解作安乐之矣。乐字于顺字。微似侵一位。何则。乐则犹有心。顺则都无事。如何。
窃谓乐字。不必手舞足蹈然后为乐。只安处便是乐。且上文既说和乐且湛。乐尔妻孥。则父母独无乐底意思乎。此等处。且当依见成说。玩味寻绎。恐不必如此费力看也。且爱说有心无心。亦恐有病。心只是活物。不可都无思虑。都无作为。但当无邪思妄为耳。此儒释所分界处。幸乞垂照如何。
鬼神章。是说天地阴阳屈伸之妙。若人鬼则与此不同而却说祭祀事于此章。恐硬。然此则陈氏已言之。其曰使天下之人之使字。尤所未晓。祭祀是子孙不忍之意。岂祖考精神使之然欤。使字之义。分明指教。
窃谓人鬼亦是天地阴阳屈伸之气。非别有一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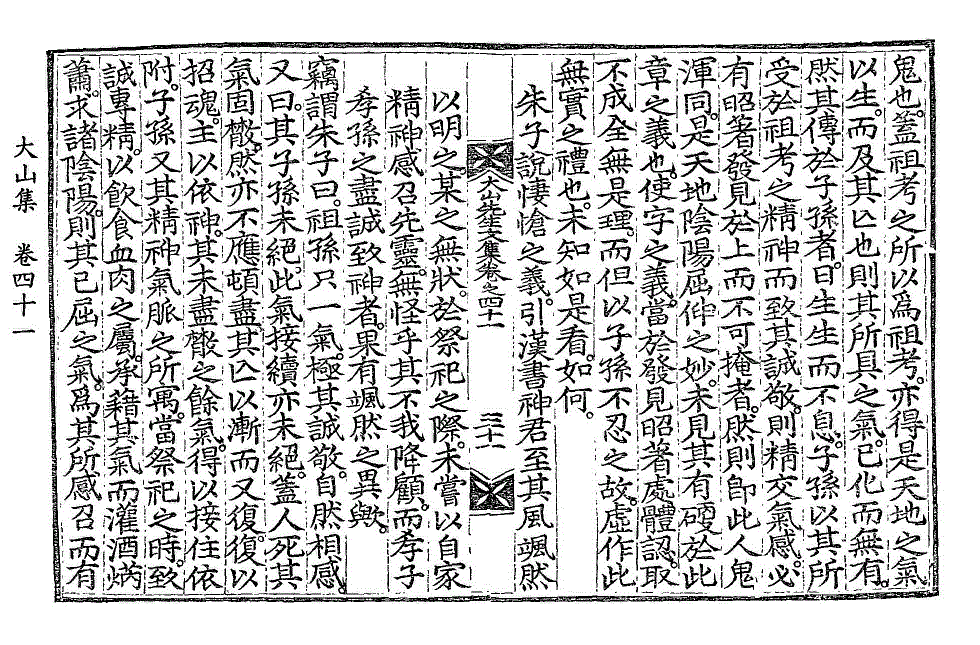 鬼也。盖祖考之所以为祖考。亦得是天地之气以生。而及其亡也则其所具之气。已化而无有。然其传于子孙者。日生生而不息。子孙以其所受于祖考之精神而致其诚敬。则精交气感。必有昭著发见于上而不可掩者。然则即此人鬼浑同。是天地阴阳屈伸之妙。未见其有硬于此章之义也。使字之义。当于发见昭著处体认。取不成全无是理。而但以子孙不忍之故。虚作此无实之礼也。未知如是看。如何。
鬼也。盖祖考之所以为祖考。亦得是天地之气以生。而及其亡也则其所具之气。已化而无有。然其传于子孙者。日生生而不息。子孙以其所受于祖考之精神而致其诚敬。则精交气感。必有昭著发见于上而不可掩者。然则即此人鬼浑同。是天地阴阳屈伸之妙。未见其有硬于此章之义也。使字之义。当于发见昭著处体认。取不成全无是理。而但以子孙不忍之故。虚作此无实之礼也。未知如是看。如何。朱子说悽怆之义。引汉书神君至其风飒然以明之。某之无状。于祭祀之际。未尝以自家精神感召先灵。无怪乎其不我降顾。而孝子孝孙之尽诚致神者。果有飒然之异欤。
窃谓朱子曰。祖孙只一气。极其诚敬。自然相感。又曰。其子孙未绝。此气接续亦未绝。盖人死其气固散。然亦不应顿尽。其亡以渐而又复。复以招魂。主以依神。其未尽散之馀气。得以接住依附。子孙又其精神气脉之所寓。当祭祀之时。致诚专精。以饮食血肉之属。承藉其气而灌酒焫萧。求诸阴阳。则其已屈之气。为其所感召而有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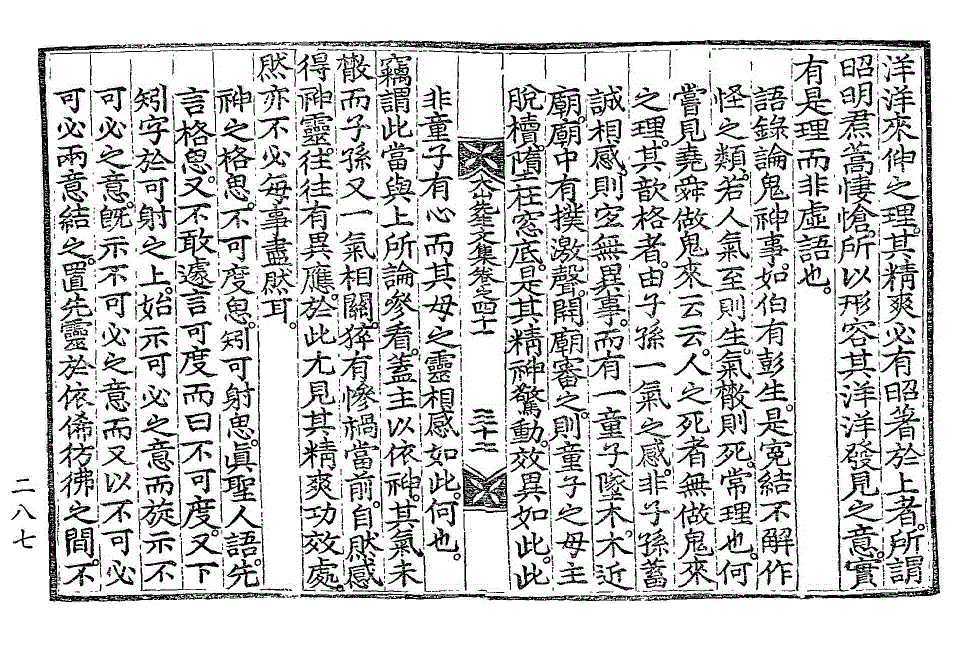 洋洋来伸之理。其精爽必有昭著于上者。所谓昭明焄蒿悽怆。所以形容其洋洋发见之意。实有是理而非虚语也。
洋洋来伸之理。其精爽必有昭著于上者。所谓昭明焄蒿悽怆。所以形容其洋洋发见之意。实有是理而非虚语也。语录论鬼神事。如伯有彭生。是冤结不解作怪之类。若人气至则生。气散则死。常理也。何尝见尧舜做鬼来云云。人之死者无做鬼来之理。其歆格者。由子孙一气之感。非子孙蓄诚相感。则宜无异事。而有一童子坠木。木近庙。庙中有扑激声。开庙审之。则童子之母主脱椟。堕在窗底。是其精神惊动。效异如此。此非童子有心而其母之灵相感如此。何也。
窃谓此当与上所论参看。盖主以依神。其气未散而子孙又一气相关。猝有惨祸当前。自然感得神灵。往往有异应。于此尤见其精爽功效处。然亦不必每事尽然耳。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真圣人语。先言格思。又不敢遽言可度而曰不可度。又下矧字于可射之上。始示可必之意而旋示不可必之意。既示不可必之意而又以不可必可必两意结之。置先灵于依俙彷佛之间。不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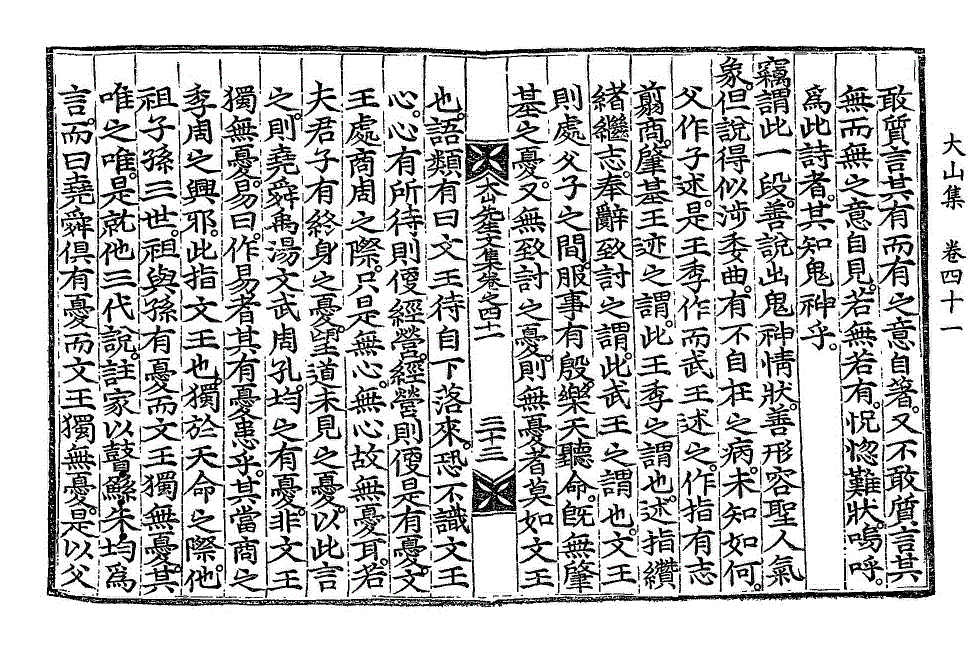 敢质言其有而有之意自著。又不敢质言其无而无之意自见。若无若有。恍惚难状。呜呼。为此诗者。其知鬼神乎。
敢质言其有而有之意自著。又不敢质言其无而无之意自见。若无若有。恍惚难状。呜呼。为此诗者。其知鬼神乎。窃谓此一段。善说出鬼神情状。善形容圣人气象。但说得似涉委曲。有不自在之病。未知如何。
父作子述。是王季作而武王述之。作指有志剪商。肇基王迹之谓。此王季之谓也。述指缵绪继志。奉辞致讨之谓。此武王之谓也。文王则处父子之间。服事有殷。乐天听命。既无肇基之忧。又无致讨之忧。则无忧者莫如文王也。语类有曰文王待自下落来。恐不识文王心。心有所待则便经营。经营则便是有忧。文王处商周之际。只是无心。无心故无忧耳。若夫君子有终身之忧。望道未见之忧。以此言之。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均之有忧。非文王独无忧。易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当商之季周之兴邪。此指文王也。独于天命之际。他祖子孙三世。祖与孙有忧而文王独无忧。其唯之唯。是就他三代说。注家以瞽,鲧,朱,均为言。而曰尧舜俱有忧而文王独无忧。是以父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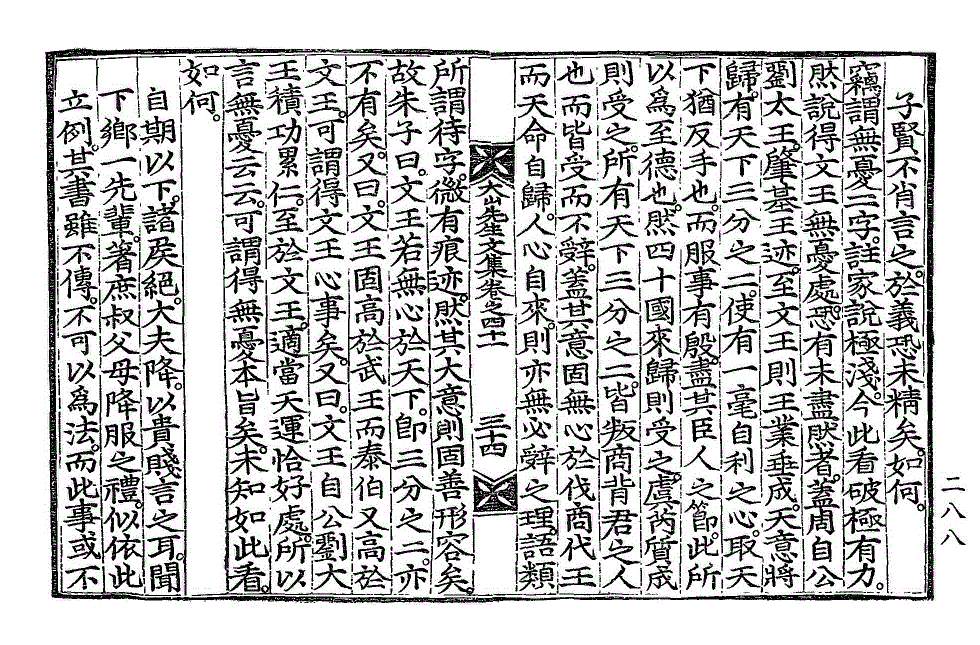 子贤不肖言之。于义恐未精矣。如何。
子贤不肖言之。于义恐未精矣。如何。窃谓无忧二字。注家说极浅。今此看破极有力。然说得文王无忧处。恐有未尽然者。盖周自公刘太王。肇基王迹。至文王则王业垂成。天意将归。有天下三分之二。使有一毫自利之心。取天下犹反手也。而服事有殷。尽其臣人之节。此所以为至德也。然四十国来归则受之。虞芮质成则受之。所有天下三分之二。皆叛商背君之人也而皆受而不辞。盖其意固无心于伐商代王而天命自归。人心自来。则亦无必辞之理。语类所谓待字。微有痕迹。然其大意则固善形容矣。故朱子曰。文王若无心于天下。即三分之二。亦不有矣。又曰。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又高于文王。可谓得文王心事矣。又曰。文王自公刘大王积功累仁。至于文王。适当天运恰好处。所以言无忧云云。可谓得无忧本旨矣。未知如此看。如何。
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以贵贱言之耳。闻下乡一先辈。著庶叔父母降服之礼。似依此立例。其书虽不传。不可以为法。而此事或不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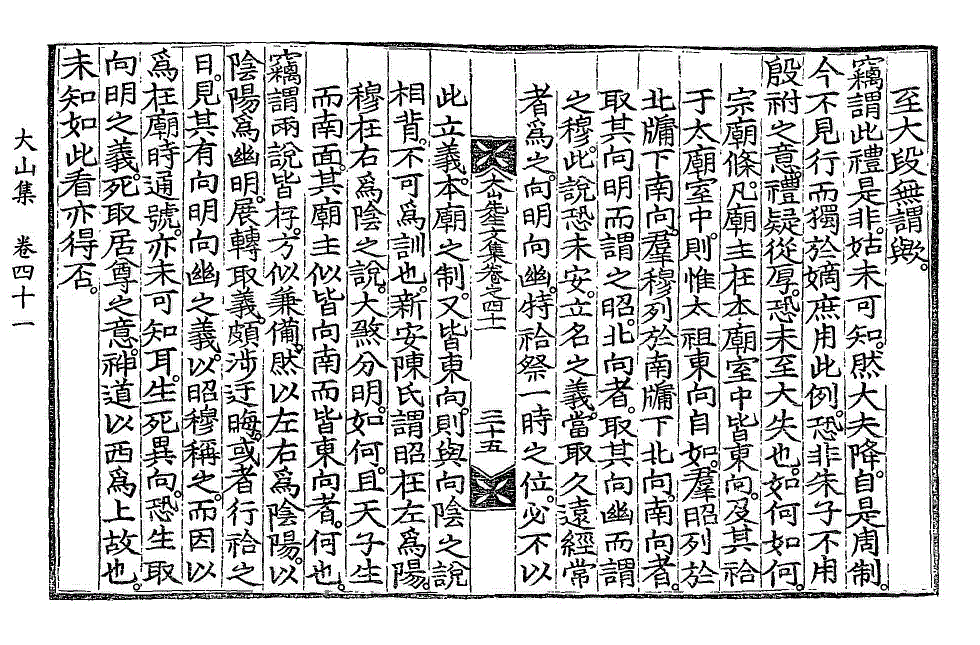 至大段无谓欤。
至大段无谓欤。窃谓此礼是非。姑未可知。然大夫降。自是周制。今不见行而独于嫡庶用此例。恐非朱子不用殷祔之意。礼疑从厚。恐未至大失也。如何如何。
宗庙条。凡庙主在本庙室中皆东向。及其祫于太庙室中。则惟太祖东向自如。群昭列于北牖下南向。群穆列于南牖下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而谓之昭。北向者。取其向幽而谓之穆。此说恐未安。立名之义。当取久远经常者为之。向明向幽。特祫祭一时之位。必不以此立义。本庙之制。又皆东向。则与向阴之说相背。不可为训也。新安陈氏谓昭在左为阳。穆在右为阴之说。大煞分明。如何。且天子生而南面。其庙主似皆向南而皆东向者。何也。
窃谓两说皆存。方似兼备。然以左右为阴阳。以阴阳为幽明。展转取义。颇涉迂晦。或者行祫之日。见其有向明向幽之义。以昭穆称之。而因以为在庙时通号。亦未可知耳。生死异向。恐生取向明之义。死取居尊之意。神道以西为上故也。未知如此看亦得否。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89L 页
 宗庙位数。说者多是。刘歆朱子。亦以为然云云。我国士大夫。皆祭四代。则已失大夫三庙之制。而其有不迁之主者。又祭五世曰。以不迁之主而祧高祖。则非 国家许置不迁位之义。皆祭五代。则便五庙也。然则天子法当立九庙。诸侯法当立七庙欤。
宗庙位数。说者多是。刘歆朱子。亦以为然云云。我国士大夫。皆祭四代。则已失大夫三庙之制。而其有不迁之主者。又祭五世曰。以不迁之主而祧高祖。则非 国家许置不迁位之义。皆祭五代。则便五庙也。然则天子法当立九庙。诸侯法当立七庙欤。窃谓古者庙各异宫。故祭三代者。不别立高祖庙。祭时旋设位。讫而除之。程朱既以高祖有服不可不祭。而今庙不异宫。排安四位于一室之内。恐不可以此为失三庙之制也。不迁位一节。实有难处。曾见沙溪说。高祖当祧。安别庙以避祭五之嫌。而旅轩先生谓不迁位不当在四代之数。恐当从此说也。如何。
社则自侯国以至于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社既祭后土。则庶人之社。皆祭后土欤。所谓里中社鸡豚社。皆为祭地而设欤。
窃谓记月令。仲春择元日命民社。郊特牲曰。唯为社事单出里。据此则古者里各有社。以祭其土之神。后世其礼遂废而里社之名犹存。意或古者祭社之日。一里之人。尽出给事。因以所祭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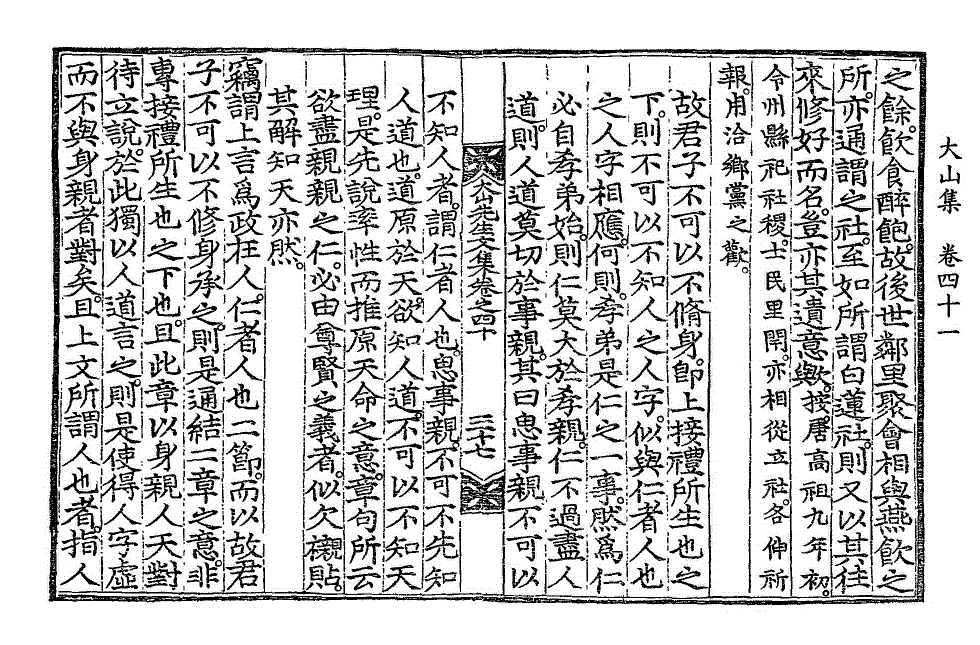 之馀。饮食醉饱。故后世邻里聚会相与燕饮之所。亦通谓之社。至如所谓白莲社。则又以其往来修好而名。岂亦其遗意欤。(按。唐高祖九年初。令州县祀社稷。士民里闬。亦相从立社。各伸祈报。用洽乡党之欢。)
之馀。饮食醉饱。故后世邻里聚会相与燕饮之所。亦通谓之社。至如所谓白莲社。则又以其往来修好而名。岂亦其遗意欤。(按。唐高祖九年初。令州县祀社稷。士民里闬。亦相从立社。各伸祈报。用洽乡党之欢。)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即上接礼所生也之下。则不可以不知人之人字。似与仁者人也之人字相应。何则。孝弟是仁之一事。然为仁必自孝弟始。则仁莫大于孝亲。仁不过尽人道。则人道莫切于事亲。其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者。谓仁者人也。思事亲。不可不先知人道也。道原于天。欲知人道。不可以不知天理。是先说率性而推原天命之意。章句所云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者。似欠衬贴。其解知天亦然。
窃谓上言为政在人。仁者人也二节。而以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承之。则是通结二章之意。非专接礼所生也之下也。且此章以身亲人天对待立说。于此独以人道言之。则是使得人字虚而不与身亲者对矣。且上文所谓人也者。指人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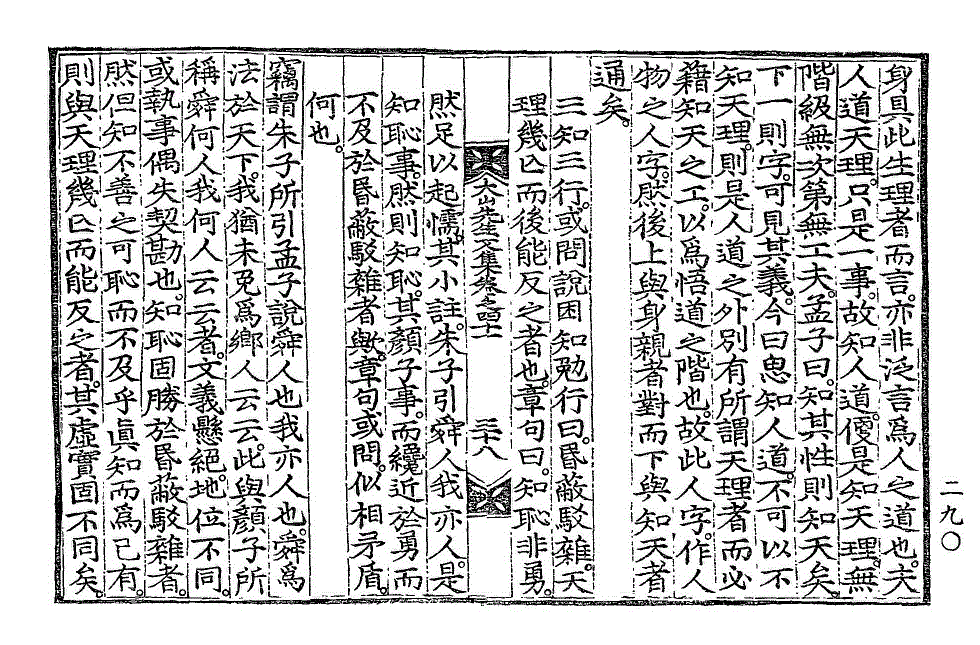 身具此生理者而言。亦非泛言为人之道也。夫人道天理。只是一事。故知人道。便是知天理。无阶级无次第无工夫。孟子曰。知其性则知天矣。下一则字。可见其义。今曰思知人道。不可以不知天理。则是人道之外别有所谓天理者而必藉知天之工。以为悟道之阶也。故此人字。作人物之人字。然后上与身亲者对而下与知天者通矣。
身具此生理者而言。亦非泛言为人之道也。夫人道天理。只是一事。故知人道。便是知天理。无阶级无次第无工夫。孟子曰。知其性则知天矣。下一则字。可见其义。今曰思知人道。不可以不知天理。则是人道之外别有所谓天理者而必藉知天之工。以为悟道之阶也。故此人字。作人物之人字。然后上与身亲者对而下与知天者通矣。三知三行。或问说困知勉行曰。昏蔽驳杂。天理几亡而后能反之者也。章句曰。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其小注。朱子引舜人我亦人。是知耻事。然则知耻。其颜子事。而才近于勇而不及于昏蔽驳杂者欤。章句或问。似相矛盾。何也。
窃谓朱子所引孟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我犹未免为乡人云云。此与颜子所称舜何人我何人云云者。文义悬绝。地位不同。或执事偶失契勘也。知耻固胜于昏蔽驳杂者。然但知不善之可耻而不及乎真知而为己有。则与天理几亡而能反之者。其虚实固不同矣。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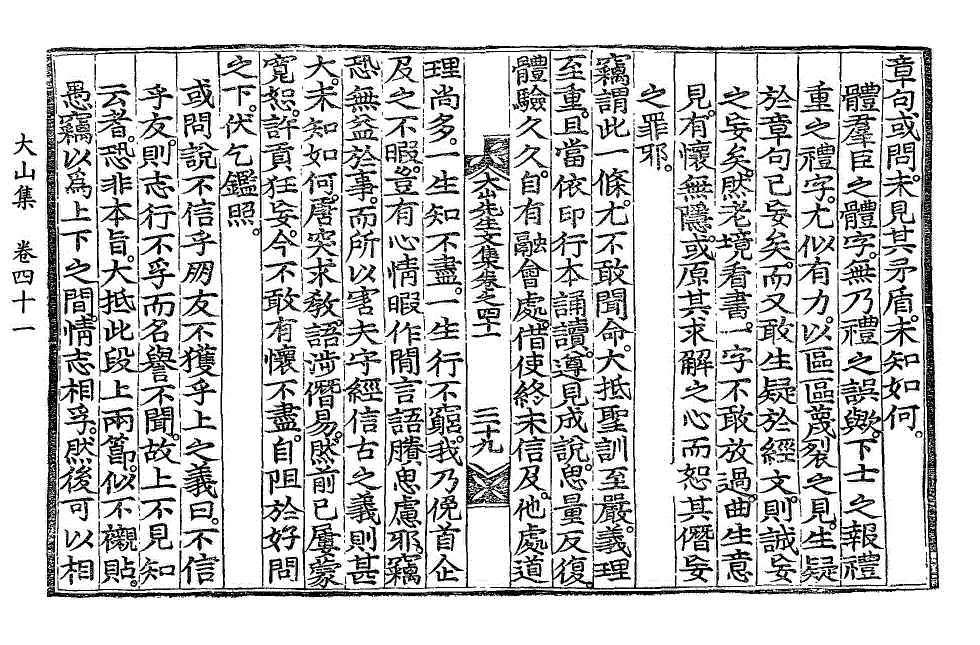 章句或问。未见其矛盾。未知如何。
章句或问。未见其矛盾。未知如何。体群臣之体字。无乃礼之误欤。下士之报礼重之礼字。尤似有力。以区区蔑裂之见。生疑于章句已妄矣。而又敢生疑于经文。则诚妄之妄矣。然老境看书。一字不敢放过。曲生意见。有怀无隐。或原其求解之心而恕其僭妄之罪邪。
窃谓此一条。尤不敢闻命。大抵圣训至严。义理至重。且当依印行本诵读。遵见成说。思量反复。体验久久。自有融会处。借使终未信及。他处道理尚多。一生知不尽。一生行不穷。我乃俛首企及之不暇。岂有心情暇作閒言语剩思虑邪。窃恐无益于事。而所以害夫守经信古之义则甚大。未知如何。唐突求教。语涉僭易。然前已屡蒙宽恕。许贡狂妄。今不敢有怀不尽。自阻于好问之下。伏乞鉴照。
或问说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之义曰。不信乎友。则志行不孚而名誉不闻。故上不见知云者。恐非本旨。大抵此段上两节。似不衬贴。愚窃以为上下之间。情志相孚。然后可以相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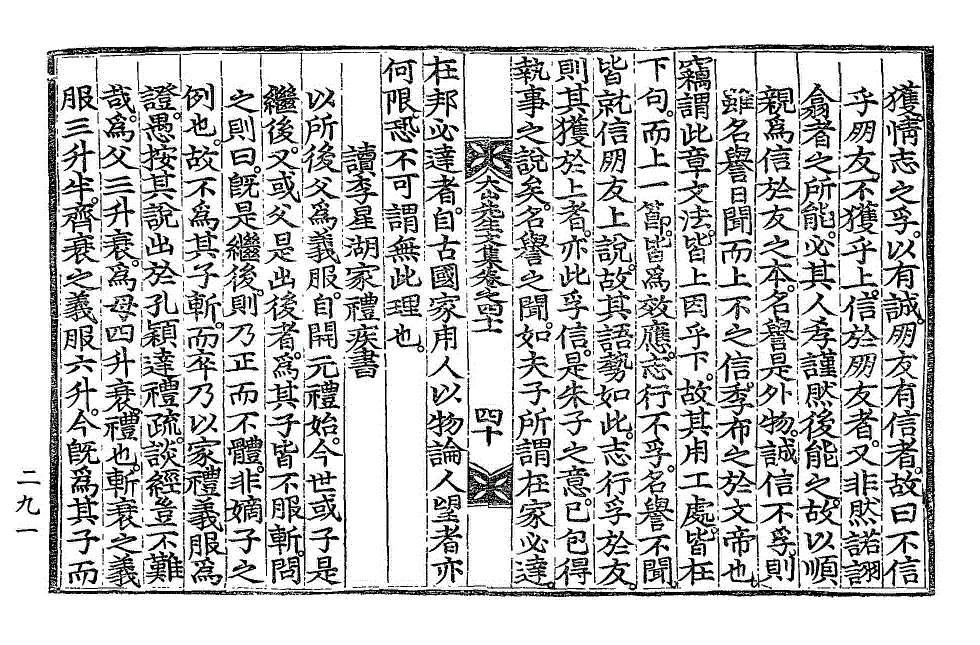 获。情志之孚。以有诚。朋友有信者。故曰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信于朋友者。又非然诺诩翕者之所能。必其人孝谨然后能之。故以顺亲为信于友之本。名誉是外物。诚信不孚。则虽名誉日闻而上不之信。季布之于文帝也。
获。情志之孚。以有诚。朋友有信者。故曰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信于朋友者。又非然诺诩翕者之所能。必其人孝谨然后能之。故以顺亲为信于友之本。名誉是外物。诚信不孚。则虽名誉日闻而上不之信。季布之于文帝也。窃谓此章文法。皆上因乎下。故其用工处。皆在下句。而上一节。皆为效应。志行不孚。名誉不闻。皆就信朋友上说。故其语势如此。志行孚于友。则其获于上者。亦此孚信。是朱子之意。已包得执事之说矣。名誉之闻。如夫子所谓在家必达。在邦必达者。自古国家用人以物论人望者亦何限。恐不可谓无此理也。
读李星湖家礼疾书
以所后父为义服。自开元礼始。今世或子是继后。又或父是出后者。为其子皆不服斩。问之则曰。既是继后。则乃正而不体。非嫡子之例也。故不为其子斩。而卒乃以家礼义服为證。愚按其说出于孔颖达礼疏。谈经岂不难哉。为父三升衰。为母四升衰。礼也。斩衰之义服三升半。齐衰之义服六升。今既为其子而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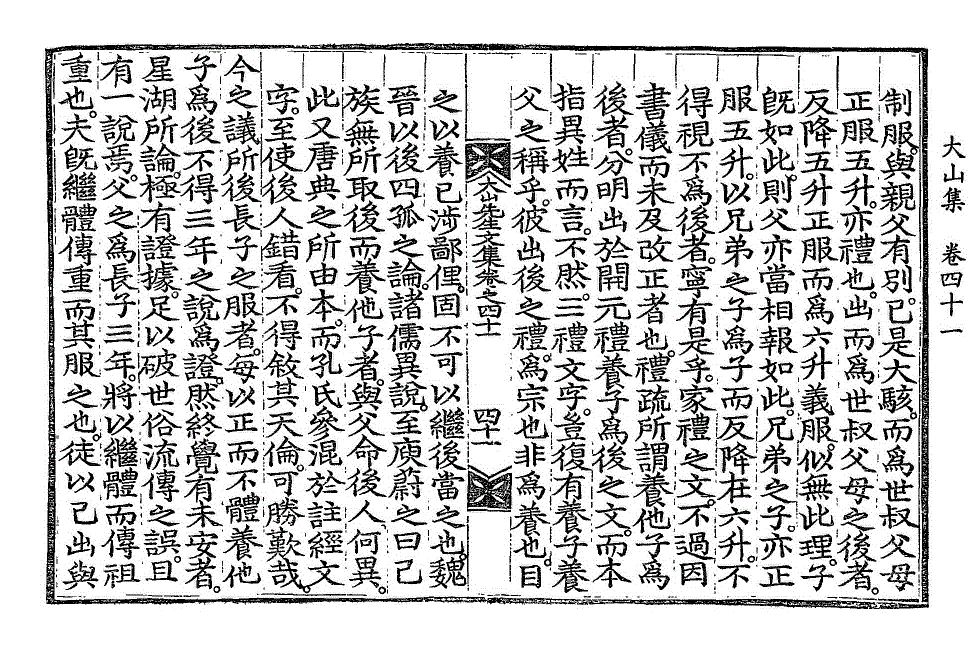 制服。与亲父有别。已是大骇。而为世叔父母正服五升。亦礼也。出而为世叔父母之后者。反降五升正服而为六升义服。似无此理。子既如此。则父亦当相报如此。兄弟之子。亦正服五升。以兄弟之子为子而反降在六升。不得视不为后者。宁有是乎。家礼之文。不过因书仪而未及改正者也。礼疏所谓养他子为后者。分明出于开元礼养子为后之文。而本指异姓而言。不然。三礼文字。岂复有养子养父之称乎。彼出后之礼。为宗也非为养也。目之以养已涉鄙俚。固不可以继后当之也。魏晋以后四孤之论。诸儒异说。至庾蔚之曰己族无所取后而养他子者。与父命后人何异。此又唐典之所由本。而孔氏参混于注经文字。至使后人错看。不得叙其天伦。可胜叹哉。
制服。与亲父有别。已是大骇。而为世叔父母正服五升。亦礼也。出而为世叔父母之后者。反降五升正服而为六升义服。似无此理。子既如此。则父亦当相报如此。兄弟之子。亦正服五升。以兄弟之子为子而反降在六升。不得视不为后者。宁有是乎。家礼之文。不过因书仪而未及改正者也。礼疏所谓养他子为后者。分明出于开元礼养子为后之文。而本指异姓而言。不然。三礼文字。岂复有养子养父之称乎。彼出后之礼。为宗也非为养也。目之以养已涉鄙俚。固不可以继后当之也。魏晋以后四孤之论。诸儒异说。至庾蔚之曰己族无所取后而养他子者。与父命后人何异。此又唐典之所由本。而孔氏参混于注经文字。至使后人错看。不得叙其天伦。可胜叹哉。今之议所后长子之服者。每以正而不体养他子为后不得三年之说为證。然终觉有未安者。星湖所论。极有證据。足以破世俗流传之误。且有一说焉。父之为长子三年。将以继体而传祖重也。夫既继体传重而其服之也。徒以己出与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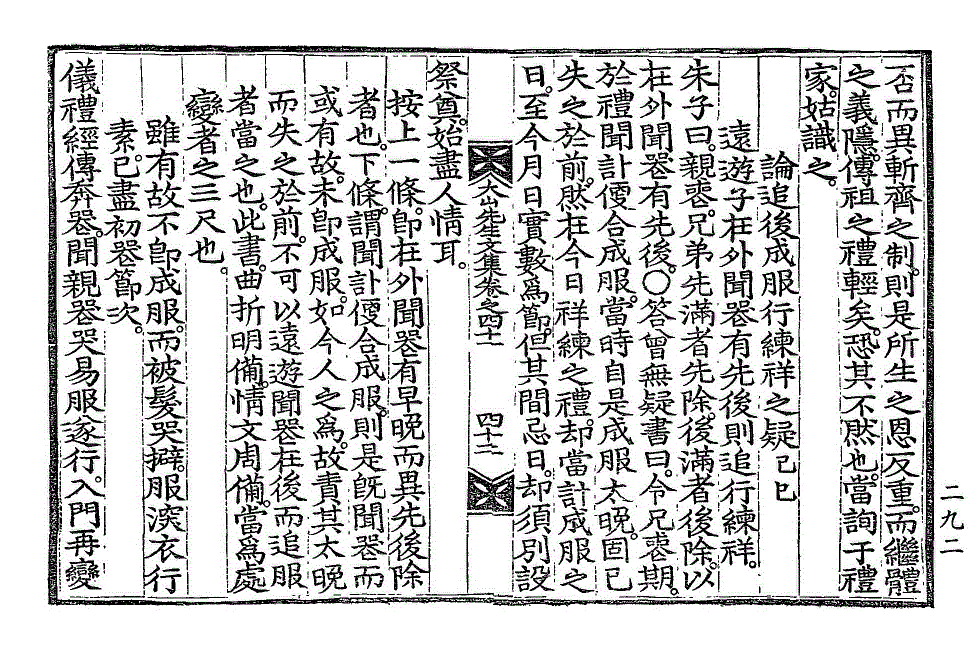 否而异斩齐之制。则是所生之恩反重。而继体之义隐。传祖之礼轻矣。恐其不然也。当询于礼家。姑识之。
否而异斩齐之制。则是所生之恩反重。而继体之义隐。传祖之礼轻矣。恐其不然也。当询于礼家。姑识之。论追后成服行练祥之疑(己巳)
远游子在外闻丧有先后则追行练祥。
朱子曰。亲丧。兄弟先满者先除。后满者后除。以在外闻丧有先后。○答曾无疑书曰。令兄丧期。于礼闻讣便合成服。当时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于前。然在今日祥练之礼。却当计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实数为节。但其间忌日。却须别设祭奠。始尽人情耳。
按上一条。即在外闻丧有早晚而异先后除者也。下条。谓闻讣便合成服。则是既闻丧而或有故。未即成服。如今人之为。故责其太晚而失之于前。不可以远游闻丧在后而追服者当之也。此书。曲折明备。情文周备。当为处变者之三尺也。
虽有故不即成服。而被发哭擗。服深衣行素。已尽初丧节次。
仪礼经传奔丧。闻亲丧哭易服遂行。入门再变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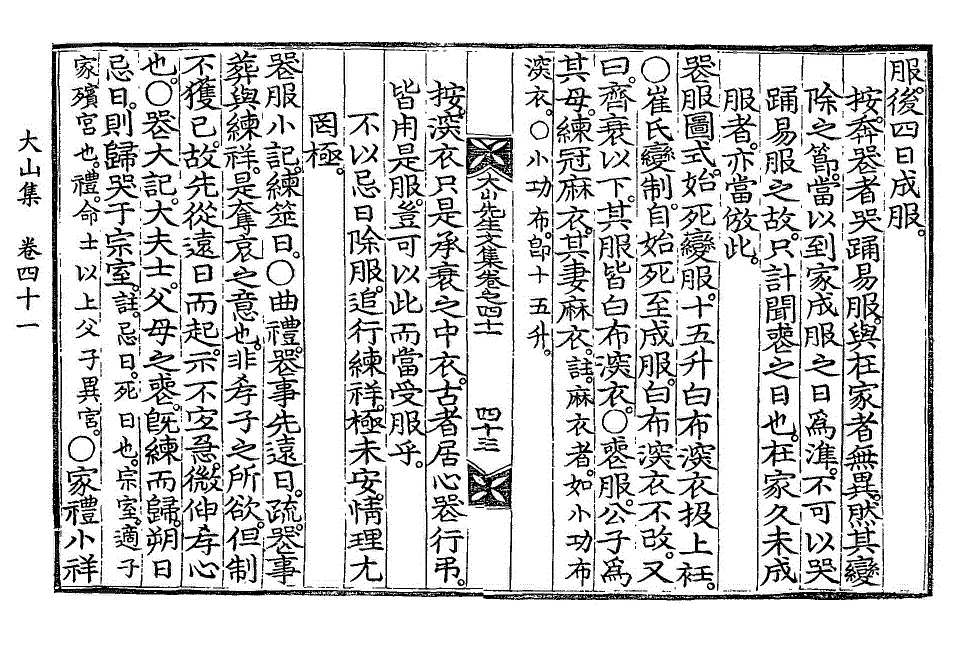 服。后四日成服。
服。后四日成服。按。奔丧者哭踊易服。与在家者无异。然其变除之节。当以到家成服之日为准。不可以哭踊易服之故。只计闻丧之日也。在家久未成服者。亦当仿此。
丧服图式。始死变服。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崔氏变制。自始死至成服。白布深衣不改。又曰。齐衰以下。其服皆白布深衣。○丧服。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其妻麻衣。(注。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小功布。即十五升。)
按。深衣只是承衰之中衣。古者居心丧行吊。皆用是服。岂可以此而当受服乎。
不以忌日除服。追行练祥。极未安。情理尤罔极。
丧服小记。练筮日。○曲礼。丧事先远日。疏。丧事葬与练祥。是夺哀之意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获已。故先从远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丧大记。大夫士。父母之丧。既练而归。朔日忌日。则归哭于宗室。(注。忌日。死日也。宗室。适子家殡宫也。礼。命士以上父子异宫。)○家礼小祥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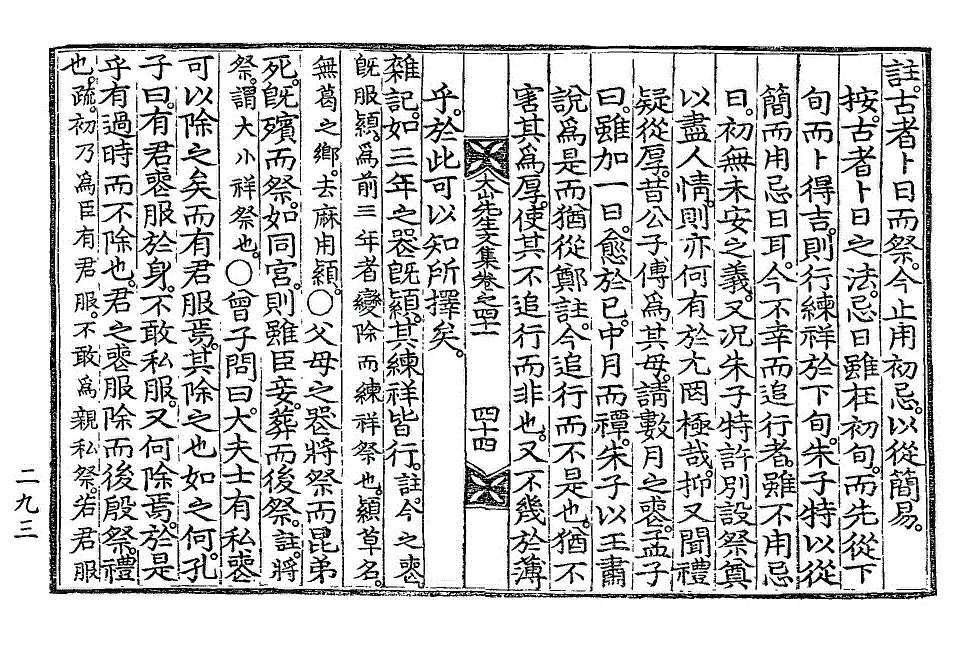 注。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从简易。
注。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从简易。按。古者卜日之法。忌日虽在初旬。而先从下旬而卜得吉。则行练祥于下旬。朱子特以从简而用忌日耳。今不幸而追行者。虽不用忌日。初无未安之义。又况朱子特许别设祭奠以尽人情。则亦何有于尤罔极哉。抑又闻礼疑从厚。昔公子傅为其母。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中月而禫。朱子以王肃说为是而犹从郑注。今追行而不是也。犹不害其为厚。使其不追行而非也。又不几于薄乎。于此可以知所择矣。
杂记。如三年之丧既顈。其练祥皆行。(注。今之丧。既服顈。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祥祭也。顈草名。无葛之乡。去麻用顈。)○父母之丧将祭而昆弟死。既殡而祭。如同宫。则虽臣妾。葬而后祭。(注。将祭。谓大小祥祭也。)○曾子问曰。大夫士有私丧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过时而不除也。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疏。初乃为臣有君服。不敢为亲私祭。若君服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4H 页
 除后乃可为亲行私丧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后。但大祥而已。)○丧服小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间。不同时而除丧。(注。孝子以事故不得治葬。中间练祥时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毕。必举练祥祭。但此二祭。仍作两次举行。如此月练祭。次月大祥。)
除后乃可为亲行私丧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后。但大祥而已。)○丧服小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间。不同时而除丧。(注。孝子以事故不得治葬。中间练祥时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毕。必举练祥祭。但此二祭。仍作两次举行。如此月练祭。次月大祥。)按。丧礼有常有变。四日而成服。三月而葬。期而练。再期而祥。其常也。或有不幸而迫于事故。不能尽如其常。则其所处者。不得不出于变。如踰时而不葬。则必葬而后除服。踰期而不能行练。则必追而练。踰再期而不能大祥。则亦追而祥。夫葬与练祥。皆有一定之期。而葬不能常则练或退。练不能常则祥或退。今成服不能常而必欲胶守祥练之期而不可移。未知其果合于处变之权矣乎。
叶味道问贱妇丧母。既葬卒哭而归。继看丧大记曰。丧父母。既练而归。贺虽令。反终其月数。而误归之月。不知尚可补填乎。朱子曰。补填。如今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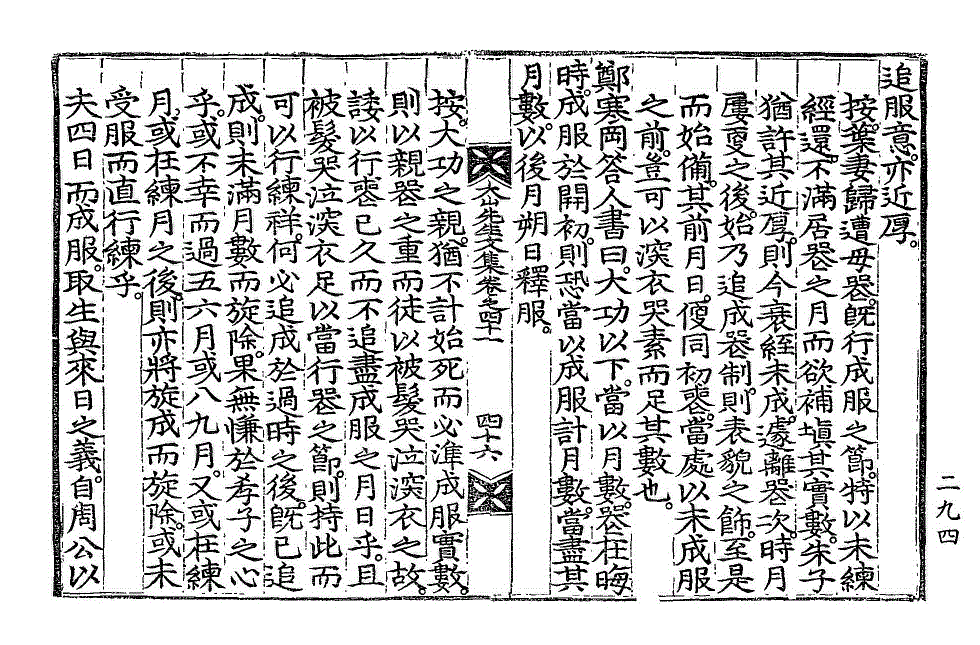 追服意。亦近厚。
追服意。亦近厚。按。叶妻归遭母丧。既行成服之节。特以未练经还。不满居丧之月而欲补填其实数。朱子犹许其近厚。则今衰绖未成。遽离丧次。时月屡更之后。始乃追成丧制。则表貌之饰。至是而始备。其前月日。便同初丧。当处以未成服之前。岂可以深衣哭素而足其数也。
郑寒冈答人书曰。大功以下。当以月数。丧在晦时。成服于开初。则恐当以成服计月数。当尽其月数。以后月朔日释服。
按。大功之亲。犹不计始死而必准成服实数。则以亲丧之重而徒以被发哭泣深衣之故。诿以行丧已久而不追尽成服之月日乎。且被发哭泣深衣足以当行丧之节。则持此而可以行练祥。何必追成于过时之后。既已追成。则未满月数而旋除。果无慊于孝子之心乎。或不幸而过五六月或八九月。又或在练月。或在练月之后。则亦将旋成而旋除。或未受服而直行练乎。
夫四日而成服。取生与来日之义。自周公以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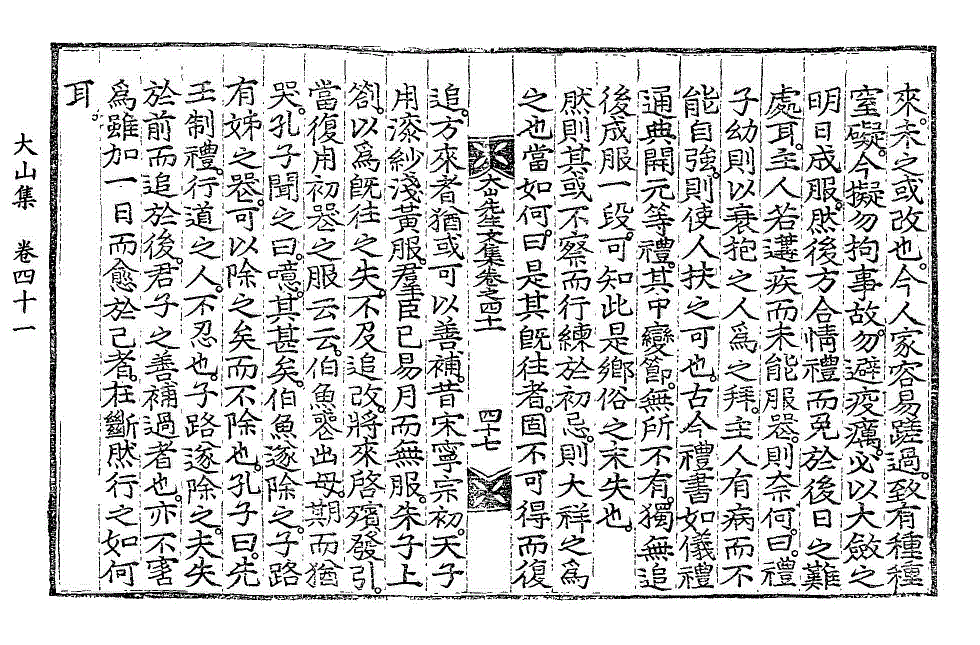 来。未之或改也。今人家容易蹉过。致有种种窒碍。今拟勿拘事故。勿避疫疠。必以大敛之明日成服。然后方合情礼而免于后日之难处耳。主人若遘疾而未能服丧。则奈何。曰。礼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主人有病而不能自强。则使人扶之可也。古今礼书如仪礼通典开元等礼。其中变节。无所不有。独无追后成服一段。可知此是乡俗之末失也。
来。未之或改也。今人家容易蹉过。致有种种窒碍。今拟勿拘事故。勿避疫疠。必以大敛之明日成服。然后方合情礼而免于后日之难处耳。主人若遘疾而未能服丧。则奈何。曰。礼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主人有病而不能自强。则使人扶之可也。古今礼书如仪礼通典开元等礼。其中变节。无所不有。独无追后成服一段。可知此是乡俗之末失也。然则其或不察而行练于初忌。则大祥之为之也当如何。曰是其既往者。固不可得而复追。方来者犹或可以善补。昔宋宁宗初。天子用漆纱浅黄服。群臣已易月而无服。朱子上劄。以为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将来启殡发引。当复用初丧之服云云。伯鱼丧出母。期而犹哭。孔子闻之曰。噫。其甚矣。伯鱼遂除之。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不除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不忍也。子路遂除之。夫失于前而追于后。君子之善补过者也。亦不害为虽加一日而愈于已者。在断然行之如何耳。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5L 页
 练祥则可追行矣。禫则奈何。曰。按丧服小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注。已祥则除。不禫。疏曰。以经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为恩念情深。不忍顿除。故有禫。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极。故不禫也。开元礼。父母之丧。周而葬者。以葬之后月小祥。其大祥则依再周之礼。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后葬者。以葬之后月练。又后月大祥。祥而即吉。无复禫矣。其未再周葬者。以二十五月练。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注。禫一月者。终二十七月之数。今以此而绵蕝焉。其或可也。(朱子答曾无疑。亦言祥练而不及禫。)
练祥则可追行矣。禫则奈何。曰。按丧服小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注。已祥则除。不禫。疏曰。以经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为恩念情深。不忍顿除。故有禫。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极。故不禫也。开元礼。父母之丧。周而葬者。以葬之后月小祥。其大祥则依再周之礼。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后葬者。以葬之后月练。又后月大祥。祥而即吉。无复禫矣。其未再周葬者。以二十五月练。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注。禫一月者。终二十七月之数。今以此而绵蕝焉。其或可也。(朱子答曾无疑。亦言祥练而不及禫。)追行大祥而与禫月偶同。则行祥于是月而禫于月中。以应古者中月之制。不亦为从厚乎。曰。此王肃说也而朱子是之。则从之固好。但练而祔。孔子既善殷。而朱子以虞卒哭。皆用周礼而祔独行殷。为未安。今练祥禫之异月而祭。尚矣。开元礼。未再周葬者。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以终二十七月之数。)再周而葬者。祥而即吉。无复禫。(假如二十五月葬。则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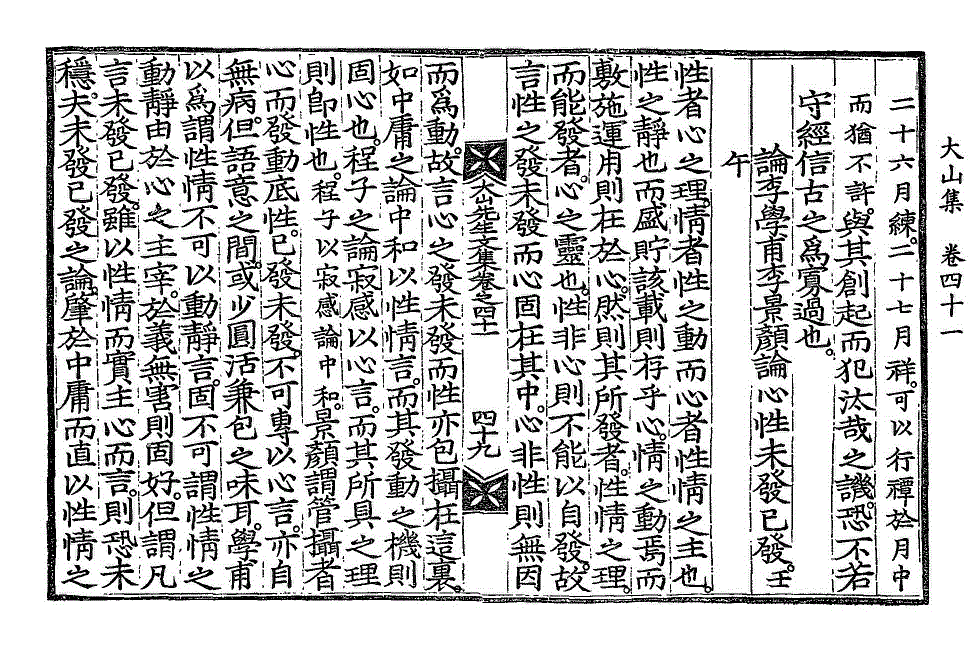 二十六月练。二十七月祥。可以行禫于月中而犹不许。)与其创起而犯汰哉之讥。恐不若守经信古之为寡过也。
二十六月练。二十七月祥。可以行禫于月中而犹不许。)与其创起而犯汰哉之讥。恐不若守经信古之为寡过也。论李学甫李景颜论心性未发已发。(壬午)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而心者性情之主也。性之静也而盛贮该载则存乎心。情之动焉而敷施运用则在于心。然则其所发者。性情之理。而能发者。心之灵也。性非心则不能以自发。故言性之发未发而心固在其中。心非性则无因而为动。故言心之发未发而性亦包摄在这里。如中庸之论中和以性情言。而其发动之机则固心也。程子之论寂感以心言。而其所具之理则即性也。(程子以寂感论中和。)景颜谓管摄者心而发动底性。已发未发。不可专以心言。亦自无病。但语意之间。或少圆活兼包之味耳。学甫以为谓性情不可以动静言。固不可谓性情之动静由于心之主宰。于义无害则固好。但谓凡言未发已发。虽以性情而实主心而言。则恐未稳。夫未发已发之论。肇于中庸而直以性情之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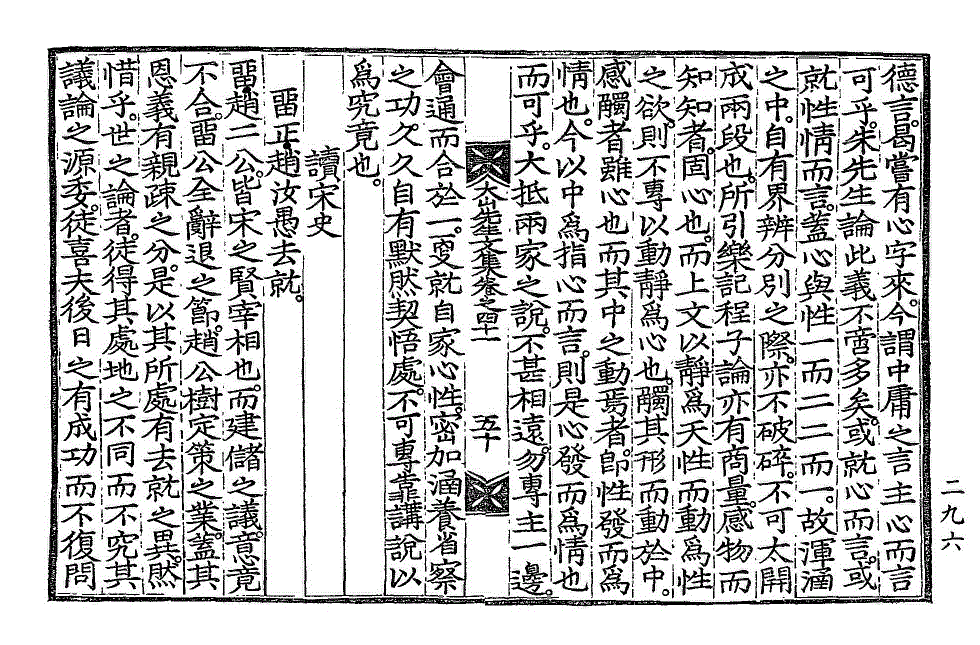 德言。曷尝有心字来。今谓中庸之言主心而言可乎。朱先生论此义不啻多矣。或就心而言。或就性情而言。盖心与性一而二二而一。故浑涵之中。自有界辨分别之际。亦不破碎。不可太开成两段也。所引乐记程子论亦有商量。感物而知知者。固心也。而上文以静为天性而动为性之欲。则不专以动静为心也。触其形而动于中。感触者虽心也而其中之动焉者。即性发而为情也。今以中为指心而言。则是心发而为情也而可乎。大抵两家之说。不甚相远。勿专主一边。会通而合于一。更就自家心性。密加涵养省察之功。久久自有默然契悟处。不可专靠讲说以为究竟也。
德言。曷尝有心字来。今谓中庸之言主心而言可乎。朱先生论此义不啻多矣。或就心而言。或就性情而言。盖心与性一而二二而一。故浑涵之中。自有界辨分别之际。亦不破碎。不可太开成两段也。所引乐记程子论亦有商量。感物而知知者。固心也。而上文以静为天性而动为性之欲。则不专以动静为心也。触其形而动于中。感触者虽心也而其中之动焉者。即性发而为情也。今以中为指心而言。则是心发而为情也而可乎。大抵两家之说。不甚相远。勿专主一边。会通而合于一。更就自家心性。密加涵养省察之功。久久自有默然契悟处。不可专靠讲说以为究竟也。读宋史
留正,赵汝愚去就。
留,赵二公。皆宋之贤宰相也。而建储之议。意竟不合。留公全辞退之节。赵公树定策之业。盖其恩义有亲疏之分。是以其所处有去就之异。然惜乎。世之论者。徒得其处地之不同而不究其议论之源委。徒喜夫后日之有成功而不复问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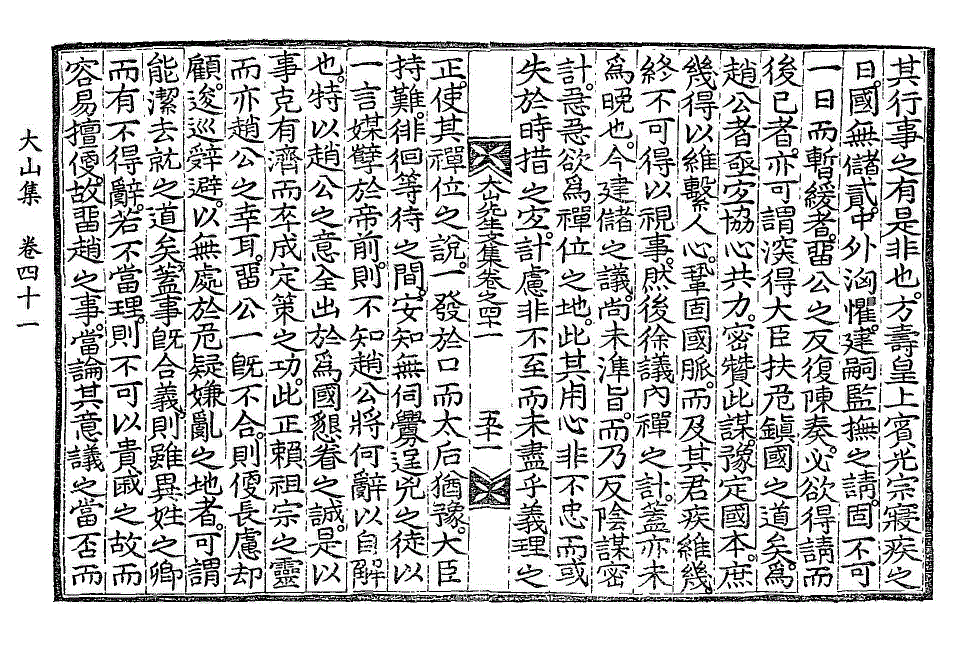 其行事之有是非也。方寿皇上宾光宗寝疾之日。国无储贰。中外汹惧。建嗣监抚之请。固不可一日而暂缓者。留公之反复陈奏。必欲得请而后已者。亦可谓深得大臣扶危镇国之道矣。为赵公者亟宜协心共力。密赞此谋。豫定国本。庶几得以维系人心。巩固国脉。而及其君疾维几。终不可得以视事。然后徐议内禅之计。盖亦未为晚也。今建储之议。尚未准旨。而乃反阴谋密计。急急欲为禅位之地。此其用心非不忠而或失于时措之宜。计虑非不至而未尽乎义理之正。使其禅位之说。一发于口而太后犹豫。大臣持难。徘徊等待之间。安知无伺衅逞凶之徒以一言媒孽于帝前。则不知赵公将何辞以自解也。特以赵公之意全出于为国恳眷之诚。是以事克有济而卒成定策之功。此正赖祖宗之灵而亦赵公之幸耳。留公一既不合。则便长虑却顾。逡巡辞避。以无处于危疑嫌乱之地者。可谓能洁去就之道矣。盖事既合义。则虽异姓之卿而有不得辞。若不当理。则不可以贵戚之故而容易擅便。故留赵之事。当论其意议之当否而
其行事之有是非也。方寿皇上宾光宗寝疾之日。国无储贰。中外汹惧。建嗣监抚之请。固不可一日而暂缓者。留公之反复陈奏。必欲得请而后已者。亦可谓深得大臣扶危镇国之道矣。为赵公者亟宜协心共力。密赞此谋。豫定国本。庶几得以维系人心。巩固国脉。而及其君疾维几。终不可得以视事。然后徐议内禅之计。盖亦未为晚也。今建储之议。尚未准旨。而乃反阴谋密计。急急欲为禅位之地。此其用心非不忠而或失于时措之宜。计虑非不至而未尽乎义理之正。使其禅位之说。一发于口而太后犹豫。大臣持难。徘徊等待之间。安知无伺衅逞凶之徒以一言媒孽于帝前。则不知赵公将何辞以自解也。特以赵公之意全出于为国恳眷之诚。是以事克有济而卒成定策之功。此正赖祖宗之灵而亦赵公之幸耳。留公一既不合。则便长虑却顾。逡巡辞避。以无处于危疑嫌乱之地者。可谓能洁去就之道矣。盖事既合义。则虽异姓之卿而有不得辞。若不当理。则不可以贵戚之故而容易擅便。故留赵之事。当论其意议之当否而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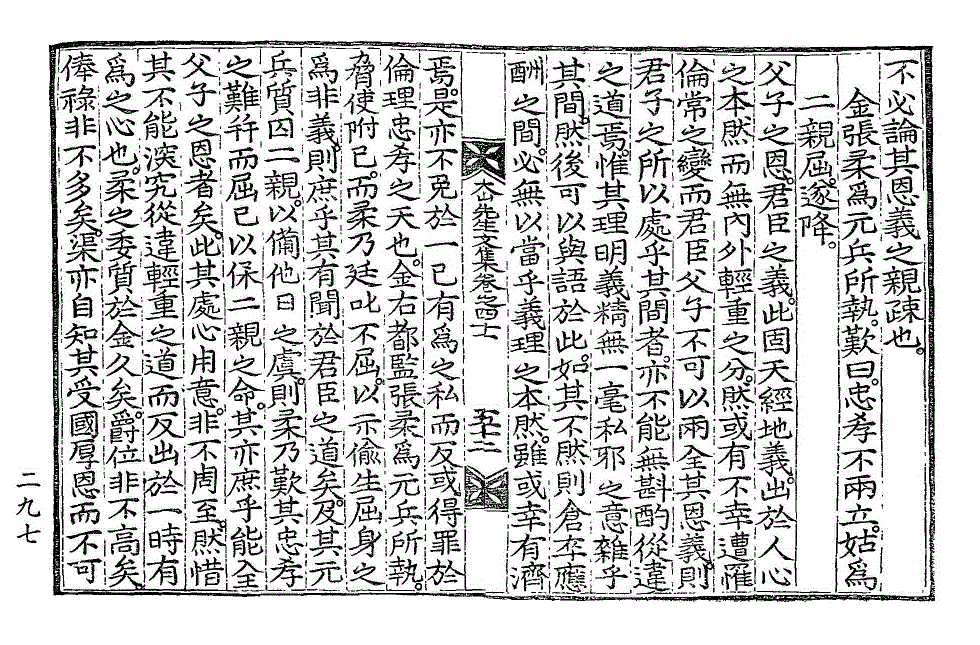 不必论其恩义之亲疏也。
不必论其恩义之亲疏也。金张柔为元兵所执。叹曰。忠孝不两立。姑为二亲屈。遂降。
父子之恩。君臣之义。此固天经地义。出于人心之本然而无内外轻重之分。然或有不幸遭罹伦常之变而君臣父子不可以两全其恩义。则君子之所以处乎其间者。亦不能无斟酌从违之道焉。惟其理明义精无一毫私邪之意杂乎其间。然后可以与语于此。如其不然则仓卒应酬之间。必无以当乎义理之本然。虽或幸有济焉。是亦不免于一己有为之私而反或得罪于伦理忠孝之天也。金右都监张柔为元兵所执。胁使附己。而柔乃廷叱不屈。以示偷生屈身之为非义。则庶乎其有闻于君臣之道矣。及其元兵质囚二亲。以备他日之虞。则柔乃叹其忠孝之难并而屈己以保二亲之命。其亦庶乎能全父子之恩者矣。此其处心用意。非不周至。然惜其不能深究从违轻重之道而反出于一时有为之心也。柔之委质于金久矣。爵位非不高矣。俸禄非不多矣。渠亦自知其受国厚恩而不可
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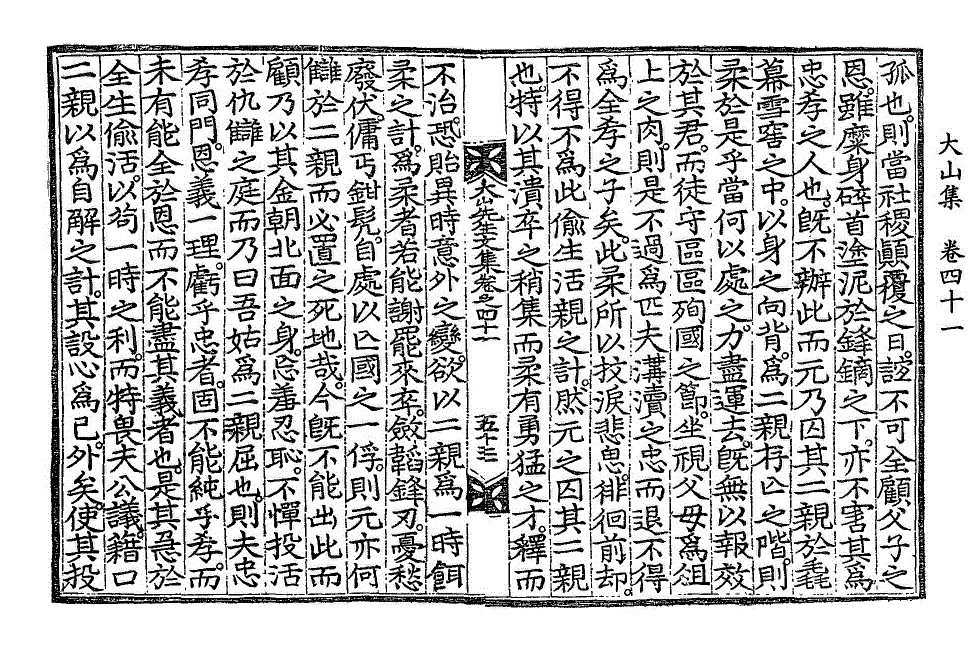 孤也。则当社稷颠覆之日。谊不可全顾父子之恩。虽糜身碎首涂泥于锋镝之下。亦不害其为忠孝之人也。既不办此而元乃囚其二亲于毳幕雪窖之中。以身之向背。为二亲存亡之阶。则柔于是乎当何以处之。力尽运去。既无以报效于其君。而徒守区区殉国之节。坐视父母为俎上之肉。则是不过为匹夫沟渎之忠而退不得为全孝之子矣。此柔所以抆泪悲思。徘徊前却。不得不为此偷生活亲之计。然元之囚其二亲也。特以其溃卒之稍集而柔有勇猛之才。释而不治。恐贻异时意外之变。欲以二亲为一时饵柔之计。为柔者若能谢罢来卒。敛韬锋刃。忧愁废伏。佣丐钳髡。自处以亡国之一俘。则元亦何雠于二亲而必置之死地哉。今既不能出此而顾乃以其金朝北面之身。忘羞忍耻。不惮投活于仇雠之庭而乃曰吾姑为二亲屈也。则夫忠孝同门。恩义一理。亏乎忠者。固不能纯乎孝。而未有能全于恩而不能尽其义者也。是其急于全生偷活。以苟一时之利。而特畏夫公议。藉口二亲以为自解之计。其设心为己。外矣。使其投
孤也。则当社稷颠覆之日。谊不可全顾父子之恩。虽糜身碎首涂泥于锋镝之下。亦不害其为忠孝之人也。既不办此而元乃囚其二亲于毳幕雪窖之中。以身之向背。为二亲存亡之阶。则柔于是乎当何以处之。力尽运去。既无以报效于其君。而徒守区区殉国之节。坐视父母为俎上之肉。则是不过为匹夫沟渎之忠而退不得为全孝之子矣。此柔所以抆泪悲思。徘徊前却。不得不为此偷生活亲之计。然元之囚其二亲也。特以其溃卒之稍集而柔有勇猛之才。释而不治。恐贻异时意外之变。欲以二亲为一时饵柔之计。为柔者若能谢罢来卒。敛韬锋刃。忧愁废伏。佣丐钳髡。自处以亡国之一俘。则元亦何雠于二亲而必置之死地哉。今既不能出此而顾乃以其金朝北面之身。忘羞忍耻。不惮投活于仇雠之庭而乃曰吾姑为二亲屈也。则夫忠孝同门。恩义一理。亏乎忠者。固不能纯乎孝。而未有能全于恩而不能尽其义者也。是其急于全生偷活。以苟一时之利。而特畏夫公议。藉口二亲以为自解之计。其设心为己。外矣。使其投大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第 2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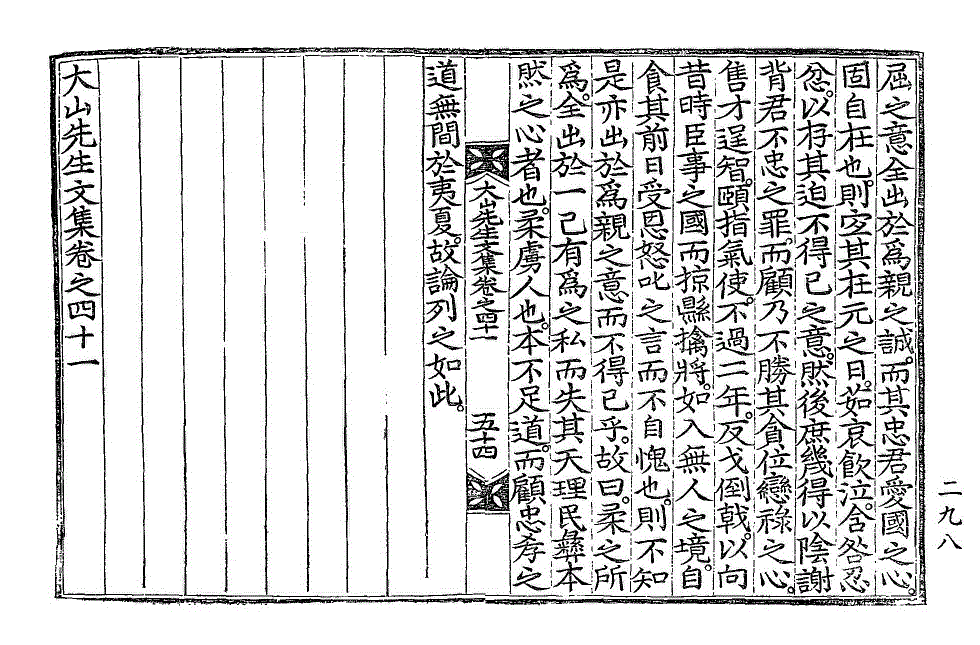 屈之意全出于为亲之诚。而其忠君爱国之心。固自在也。则宜其在元之日。茹哀饮泣。含咎忍忿。以存其迫不得已之意。然后庶几得以阴谢背君不忠之罪。而顾乃不胜其贪位恋禄之心。售才逞智。颐指气使。不过二年。反戈倒戟。以向昔时臣事之国而掠县擒将。如入无人之境。自食其前日受恩怒叱之言而不自愧也。则不知是亦出于为亲之意而不得已乎。故曰。柔之所为。全出于一己有为之私而失其天理民彝本然之心者也。柔虏人也。本不足道。而顾忠孝之道无间于夷夏。故论列之如此。
屈之意全出于为亲之诚。而其忠君爱国之心。固自在也。则宜其在元之日。茹哀饮泣。含咎忍忿。以存其迫不得已之意。然后庶几得以阴谢背君不忠之罪。而顾乃不胜其贪位恋禄之心。售才逞智。颐指气使。不过二年。反戈倒戟。以向昔时臣事之国而掠县擒将。如入无人之境。自食其前日受恩怒叱之言而不自愧也。则不知是亦出于为亲之意而不得已乎。故曰。柔之所为。全出于一己有为之私而失其天理民彝本然之心者也。柔虏人也。本不足道。而顾忠孝之道无间于夷夏。故论列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