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明美堂集卷九 第 x 页
明美堂集卷九(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书
书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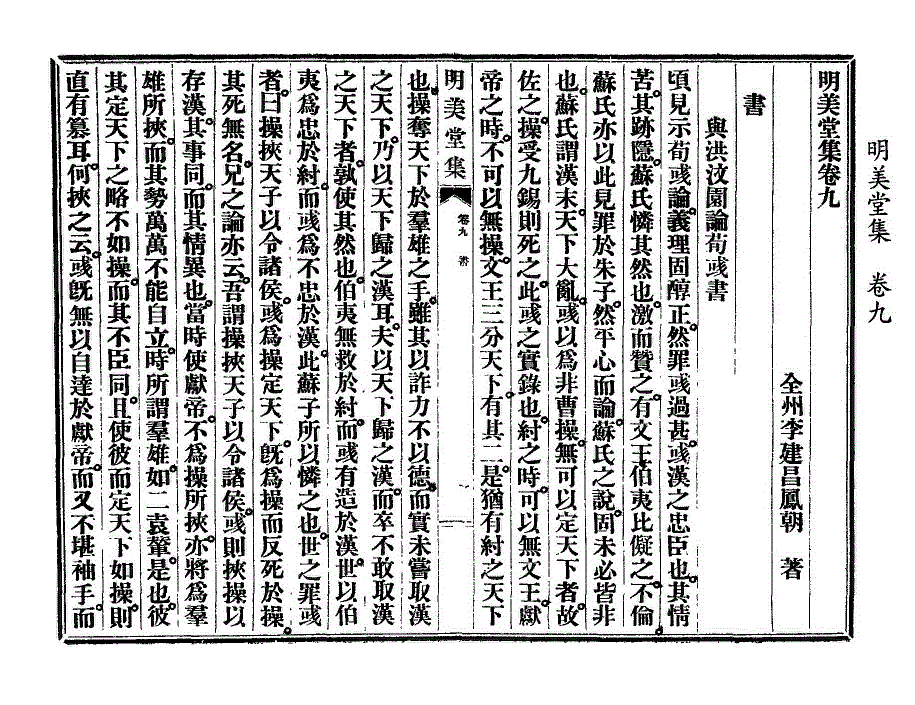 与洪汶园论荀彧书
与洪汶园论荀彧书顷见示荀彧论。义理固醇正。然罪彧过甚。彧汉之忠臣也。其情苦。其迹隐。苏氏怜其然也。激而赞之。有文王,伯夷比儗之。不伦。苏氏亦以此见罪于朱子。然平心而论。苏氏之说。固未必皆非也。苏氏谓汉末。天下大乱。彧以为非曹操。无可以定天下者。故佐之。操受九锡则死之。此彧之实录也。纣之时。可以无文王。献帝之时。不可以无操。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犹有纣之天下也。操夺天下于群雄之手。虽其以诈力不以德。而实未尝取汉之天下。乃以天下归之汉耳。夫以天下归之汉。而卒不敢取汉之天下者。孰使其然也。伯夷无救于纣。而彧有造于汉。世以伯夷为忠于纣。而彧为不忠于汉。此苏子所以怜之也。世之罪彧者。曰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彧为操定天下。既为操而反死于操。其死无名。兄之论亦云。吾谓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彧则挟操以存汉。其事同。而其情异也。当时使献帝。不为操所挟。亦将为群雄所挟。而其势万万不能自立。时所谓群雄。如二袁辇。是也。彼其定天下之略不如操。而其不臣同。且使彼而定天下如操。则直有篡耳。何挟之云。彧既无以自达于献帝。而又不堪袖手。而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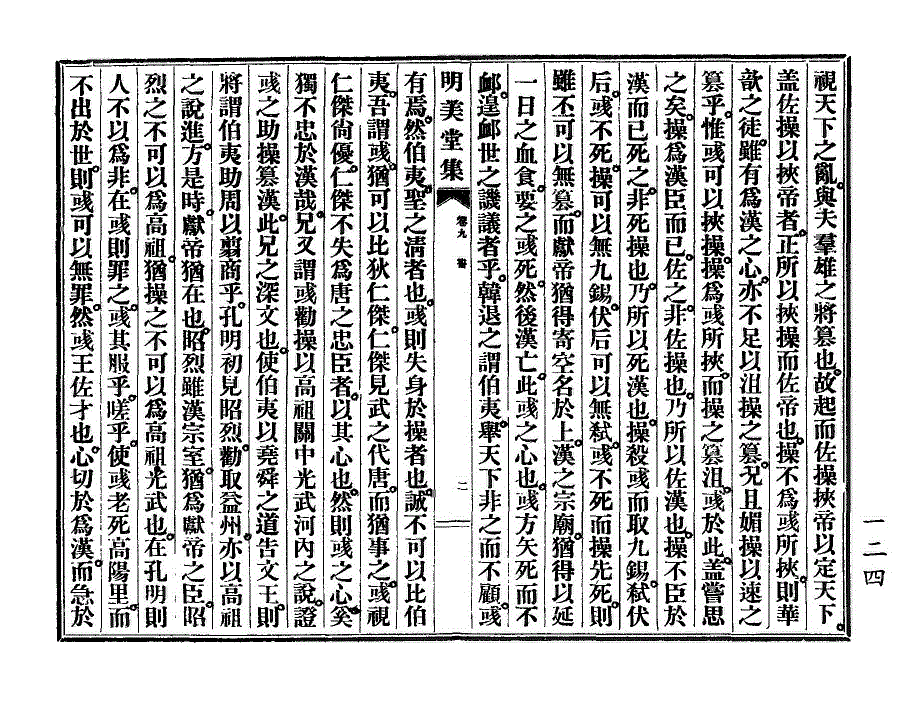 视天下之乱。与夫群雄之将篡也。故起而佐操挟帝以定天下。盖佐操以挟帝者。正所以挟操而佐帝也。操不为彧所挟。则华歆之徒。虽有为汉之心。亦不足以沮操之篡。况且媚操以速之篡乎。惟彧可以挟操。操为彧所挟。而操之篡沮。彧于此。盖尝思之矣。操为汉臣而己佐之。非佐操也。乃所以佐汉也。操不臣于汉而己死之。非死操也。乃所以死汉也。操杀彧而取九锡。弑伏后。彧不死。操可以无九锡。伏后可以无弑。彧不死而操先死。则虽丕可以无篡。而献帝犹得寄空名于上。汉之宗庙。犹得以延一日之血食。要之彧死。然后汉亡。此彧之心也。彧方矢死而不恤。遑恤世之讥议者乎。韩退之谓伯夷。举天下非之而不顾。彧有焉。然伯夷。圣之清者也。彧则失身于操者也。诚不可以比伯夷。吾谓彧。犹可以比狄仁杰。仁杰见武之代唐。而犹事之。彧视仁杰尚优。仁杰不失为唐之忠臣者。以其心也。然则彧之心。奚独不忠于汉哉。兄又谓彧劝操以高祖关中光武河内之说。證彧之助操篡汉。此兄之深文也。使伯夷以尧舜之道告文王。则将谓伯夷助周以剪商乎。孔明初见昭烈。劝取益州。亦以高祖之说进。方是时。献帝犹在也。昭烈虽汉宗室。犹为献帝之臣。诏烈之不可以为高祖。犹操之不可以为高祖,光武也。在孔明则人不以为非。在彧则罪之。彧其服乎。嗟乎。使彧老死高阳里。而不出于世。则彧可以无罪。然彧王佐才也。心切于为汉。而急于
视天下之乱。与夫群雄之将篡也。故起而佐操挟帝以定天下。盖佐操以挟帝者。正所以挟操而佐帝也。操不为彧所挟。则华歆之徒。虽有为汉之心。亦不足以沮操之篡。况且媚操以速之篡乎。惟彧可以挟操。操为彧所挟。而操之篡沮。彧于此。盖尝思之矣。操为汉臣而己佐之。非佐操也。乃所以佐汉也。操不臣于汉而己死之。非死操也。乃所以死汉也。操杀彧而取九锡。弑伏后。彧不死。操可以无九锡。伏后可以无弑。彧不死而操先死。则虽丕可以无篡。而献帝犹得寄空名于上。汉之宗庙。犹得以延一日之血食。要之彧死。然后汉亡。此彧之心也。彧方矢死而不恤。遑恤世之讥议者乎。韩退之谓伯夷。举天下非之而不顾。彧有焉。然伯夷。圣之清者也。彧则失身于操者也。诚不可以比伯夷。吾谓彧。犹可以比狄仁杰。仁杰见武之代唐。而犹事之。彧视仁杰尚优。仁杰不失为唐之忠臣者。以其心也。然则彧之心。奚独不忠于汉哉。兄又谓彧劝操以高祖关中光武河内之说。證彧之助操篡汉。此兄之深文也。使伯夷以尧舜之道告文王。则将谓伯夷助周以剪商乎。孔明初见昭烈。劝取益州。亦以高祖之说进。方是时。献帝犹在也。昭烈虽汉宗室。犹为献帝之臣。诏烈之不可以为高祖。犹操之不可以为高祖,光武也。在孔明则人不以为非。在彧则罪之。彧其服乎。嗟乎。使彧老死高阳里。而不出于世。则彧可以无罪。然彧王佐才也。心切于为汉。而急于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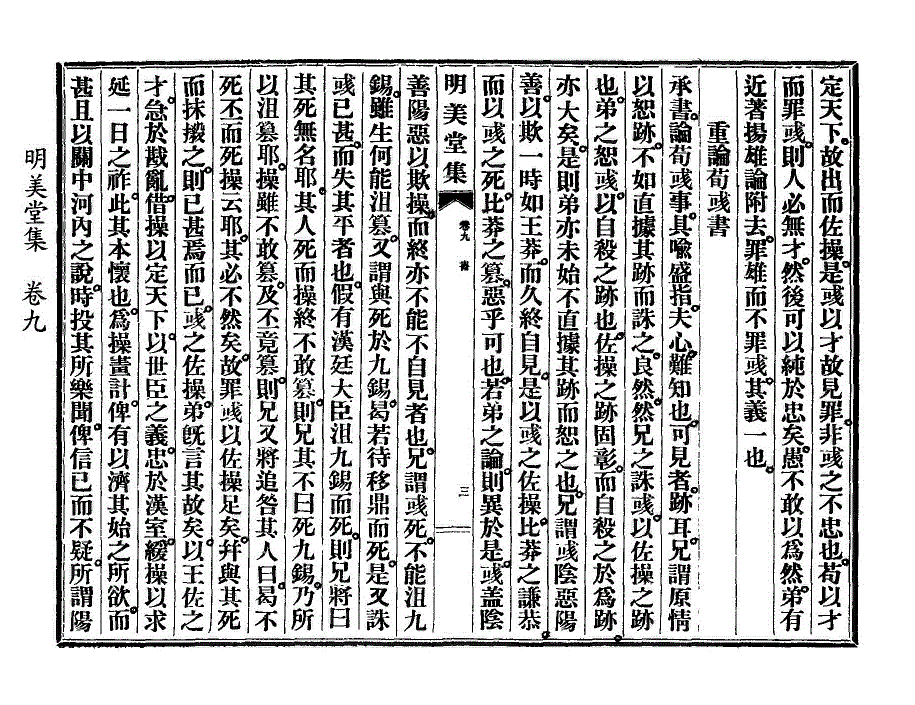 定天下。故出而佐操。是彧以才故见罪。非彧之不忠也。苟以才而罪彧。则人必无才。然后可以纯于忠矣。愚不敢以为然。弟有近著扬雄论附去。罪雄而不罪彧。其义一也。
定天下。故出而佐操。是彧以才故见罪。非彧之不忠也。苟以才而罪彧。则人必无才。然后可以纯于忠矣。愚不敢以为然。弟有近著扬雄论附去。罪雄而不罪彧。其义一也。重论荀彧书
承书。论荀彧事。具喻盛指。夫心。难知也。可见者。迹耳。兄谓原情以恕迹。不如直据其迹而诛之。良然。然兄之诛彧。以佐操之迹也。弟之恕彧。以自杀之迹也。佐操之迹固彰。而自杀之于为迹。亦大矣。是则弟亦未始不直据其迹而恕之也。兄谓彧阴恶阳善。以欺一时如王莽。而久终自见。是以彧之佐操。比莽之谦恭。而以彧之死。比莽之篡。恶乎可也。若弟之论。则异于是。彧盖阴善阳恶以欺操。而终亦不能不自见者也。兄谓彧死。不能沮九锡。虽生何能沮篡。又谓与死于九锡。曷若待移鼎而死。是又诛彧已甚。而失其平者也。假有汉廷大臣沮九锡而死。则兄将曰其死无名耶。其人死而操终不敢篡。则兄其不曰死九锡。乃所以沮篡耶。操虽不敢篡。及丕竟篡。则兄又将追咎其人曰。曷不死丕而死操云耶。其必不然矣。故罪彧以佐操足矣。并与其死而抹摋之。则已甚焉而已。彧之佐操。弟既言其故矣。以王佐之才。急于戡乱。借操以定天下。以世臣之义。忠于汉室。缓操以求延一日之祚。此其本怀也。为操画计。俾有以济其始之所欲。而甚且以关中河内之说。时投其所乐闻。俾信己而不疑。所谓阳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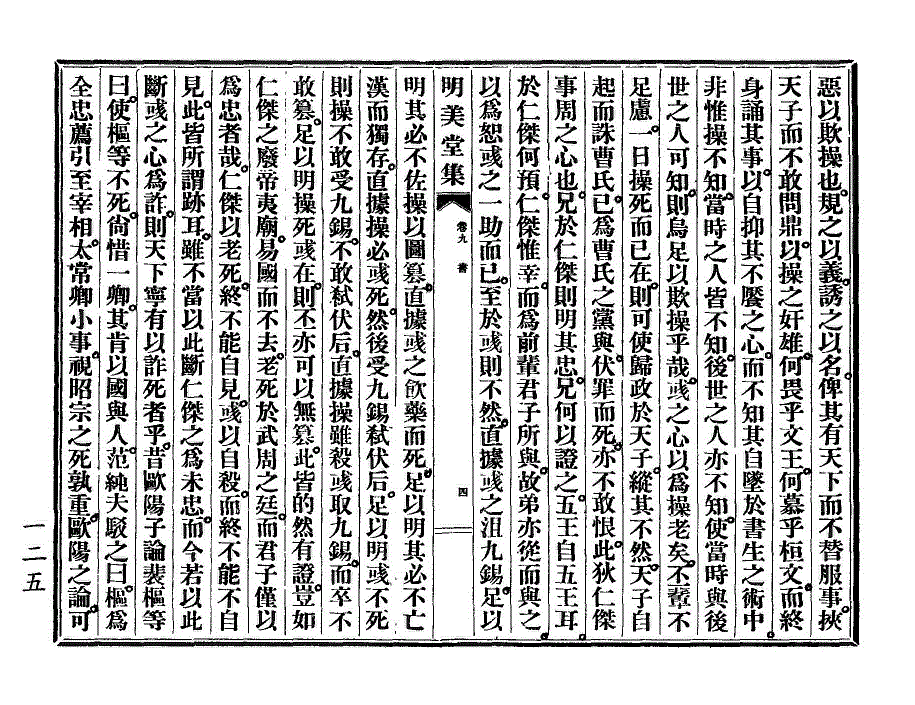 恶以欺操也。规之以义。诱之以名。俾其有天下而不替服事。挟天子而不敢问鼎。以操之奸雄。何畏乎文王。何慕乎桓文。而终身诵其事。以自抑其不餍之心。而不知其自坠于书生之术中。非惟操不知。当时之人皆不知。后世之人亦不知。使当时与后世之人可知。则乌足以欺操乎哉。彧之心以为操老矣。丕辈不足虑。一日操死而己在。则可使归政于天子。纵其不然。天子自起而诛曹氏。己为曹氏之党与。伏罪而死。亦不敢恨。此狄仁杰事周之心也。兄于仁杰则明其忠。兄何以證之。五王自五王耳。于仁杰何预。仁杰惟幸。而为前辈君子所与。故弟亦从而与之。以为恕彧之一助而已。至于彧则不然。直据彧之沮九锡。足以明其必不佐操以图篡。直据彧之饮药而死。足以明其必不亡汉而独存。直据操必彧死。然后受九锡弑伏后。足以明彧不死则操不敢受九锡。不敢弑伏后。直据操虽杀彧取九锡。而卒不敢篡。足以明操死彧在。则不亦可以无篡。此皆的然有證。岂如仁杰之废帝夷庙。易国而不去。老死于武周之廷。而君子仅以为忠者哉。仁杰以老死。终不能自见。彧以自杀。而终不能不自见。此皆所谓迹耳。虽不当以此断仁杰之为未忠。而今若以此断彧之心为诈。则天下宁有以诈死者乎。昔欧阳子论裴枢等曰。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范纯夫驳之曰。枢为全忠荐引至宰相。太常卿小事。视昭宗之死孰重。欧阳之论。可
恶以欺操也。规之以义。诱之以名。俾其有天下而不替服事。挟天子而不敢问鼎。以操之奸雄。何畏乎文王。何慕乎桓文。而终身诵其事。以自抑其不餍之心。而不知其自坠于书生之术中。非惟操不知。当时之人皆不知。后世之人亦不知。使当时与后世之人可知。则乌足以欺操乎哉。彧之心以为操老矣。丕辈不足虑。一日操死而己在。则可使归政于天子。纵其不然。天子自起而诛曹氏。己为曹氏之党与。伏罪而死。亦不敢恨。此狄仁杰事周之心也。兄于仁杰则明其忠。兄何以證之。五王自五王耳。于仁杰何预。仁杰惟幸。而为前辈君子所与。故弟亦从而与之。以为恕彧之一助而已。至于彧则不然。直据彧之沮九锡。足以明其必不佐操以图篡。直据彧之饮药而死。足以明其必不亡汉而独存。直据操必彧死。然后受九锡弑伏后。足以明彧不死则操不敢受九锡。不敢弑伏后。直据操虽杀彧取九锡。而卒不敢篡。足以明操死彧在。则不亦可以无篡。此皆的然有證。岂如仁杰之废帝夷庙。易国而不去。老死于武周之廷。而君子仅以为忠者哉。仁杰以老死。终不能自见。彧以自杀。而终不能不自见。此皆所谓迹耳。虽不当以此断仁杰之为未忠。而今若以此断彧之心为诈。则天下宁有以诈死者乎。昔欧阳子论裴枢等曰。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范纯夫驳之曰。枢为全忠荐引至宰相。太常卿小事。视昭宗之死孰重。欧阳之论。可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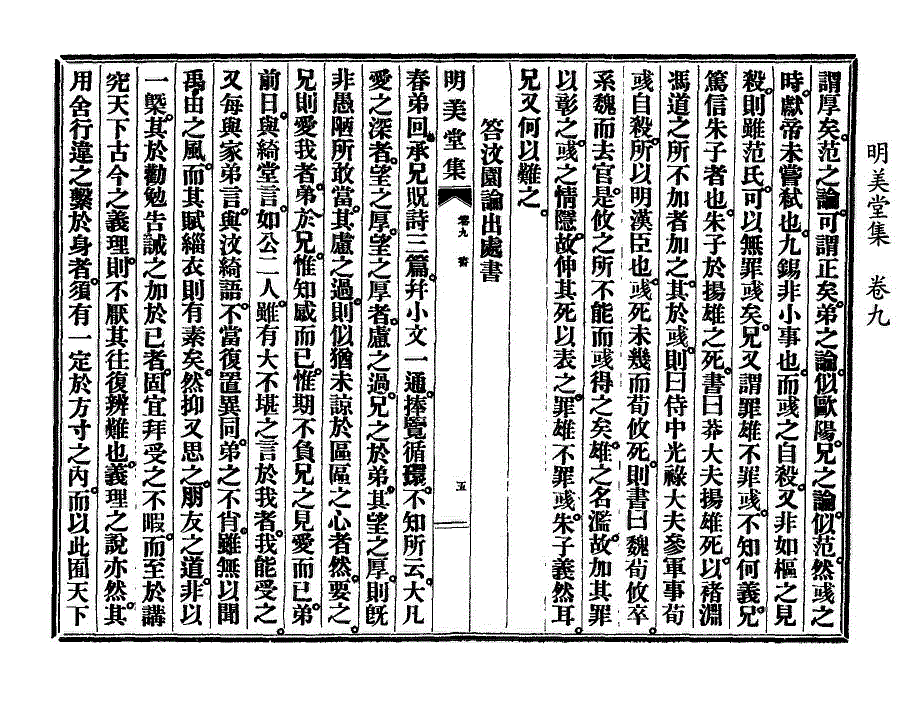 谓厚矣。范之论。可谓正矣。弟之论。似欧阳。兄之论。似范。然彧之时。献帝未尝弑也。九锡非小事也。而彧之自杀。又非如枢之见杀。则虽范氏。可以无罪彧矣。兄又谓罪雄不罪彧。不知何义。兄笃信朱子者也。朱子于扬雄之死。书曰莽大夫扬雄死。以褚渊冯道之所不加者加之。其于彧。则曰侍中光禄大夫参军事荀彧自杀。所以明汉臣也。彧死未几而荀攸死。则书曰魏荀攸卒。系魏而去官。是攸之所不能而彧得之矣。雄之名滥。故加其罪以彰之。彧之情隐。故伸其死以表之。罪雄不罪彧。朱子义然耳。兄又何以难之。
谓厚矣。范之论。可谓正矣。弟之论。似欧阳。兄之论。似范。然彧之时。献帝未尝弑也。九锡非小事也。而彧之自杀。又非如枢之见杀。则虽范氏。可以无罪彧矣。兄又谓罪雄不罪彧。不知何义。兄笃信朱子者也。朱子于扬雄之死。书曰莽大夫扬雄死。以褚渊冯道之所不加者加之。其于彧。则曰侍中光禄大夫参军事荀彧自杀。所以明汉臣也。彧死未几而荀攸死。则书曰魏荀攸卒。系魏而去官。是攸之所不能而彧得之矣。雄之名滥。故加其罪以彰之。彧之情隐。故伸其死以表之。罪雄不罪彧。朱子义然耳。兄又何以难之。答汶园论出处书
春弟回。承兄贶诗三篇。并小文一通。捧览循环。不知所云。大凡爱之深者。望之厚。望之厚者。虑之过。兄之于弟。其望之厚。则既非愚陋所敢当。其虑之过。则似犹未谅于区区之心者然。要之。兄则爱我者。弟于兄。惟知感而已。惟期不负兄之见爱而已。弟前日。与绮堂言。如公二人。虽有大不堪之言于我者。我能受之。又每与家弟言。与汶绮语。不当复置异同。弟之不肖。虽无以闻禹,由之风。而其赋缁衣则有素矣。然抑又思之。朋友之道。非以一槩。其于劝勉告诫之加于己者。固宜拜受之不暇。而至于讲究天下古今之义理。则不厌其往复辨难也。义理之说亦然。其用舍行违之系于身者。须有一定于方寸之内。而以此囿天下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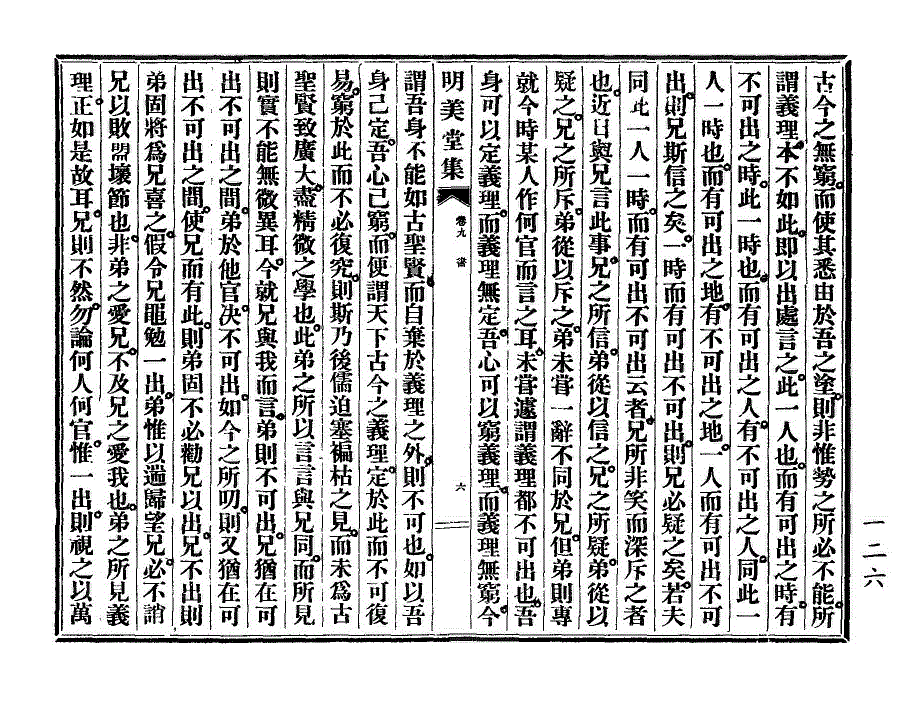 古今之无穷。而使其悉由于吾之涂。则非惟势之所必不能。所谓义理。本不如此。即以出处言之。此一人也。而有可出之时。有不可出之时。此一时也。而有可出之人。有不可出之人。同此一人一时也。而有可出之地。有不可出之地。一人而有可出不可出。则兄斯信之矣。一时而有可出不可出。则兄必疑之矣。若夫同此一人一时。而有可出不可出云者。兄所非笑而深斥之者也。近日与兄言此事。兄之所信。弟从以信之。兄之所疑。弟从以疑之。兄之所斥。弟从以斥之。弟未尝一辞不同于兄。但弟则专就今时某人作何官而言之耳。未尝遽谓义理都不可出也。吾身可以定义理。而义理无定。吾心可以穷义理。而义理无穷。今谓吾身不能如古圣贤。而自弃于义理之外。则不可也。如以吾身已定。吾心已穷。而便谓天下古今之义理。定于此而不可复易。穷于此而不必复究。则斯乃后儒迫塞褊枯之见。而未为古圣贤致广大。尽精微之学也。此弟之所以言言与兄同。而所见则实不能无微异耳。今就兄与我而言。弟则不可出。兄犹在可出不可出之间。弟于他官。决不可出。如今之所叨。则又犹在可出不可出之间。使兄而有此。则弟固不必劝兄以出。兄不出则弟固将为兄喜之。假令兄黾勉一出。弟惟以遄归望兄。必不诮兄以败盟坏节也。非弟之爱兄。不及兄之爱我也。弟之所见义理。正如是故耳。兄则不然。勿论何人何官。惟一出。则视之以万
古今之无穷。而使其悉由于吾之涂。则非惟势之所必不能。所谓义理。本不如此。即以出处言之。此一人也。而有可出之时。有不可出之时。此一时也。而有可出之人。有不可出之人。同此一人一时也。而有可出之地。有不可出之地。一人而有可出不可出。则兄斯信之矣。一时而有可出不可出。则兄必疑之矣。若夫同此一人一时。而有可出不可出云者。兄所非笑而深斥之者也。近日与兄言此事。兄之所信。弟从以信之。兄之所疑。弟从以疑之。兄之所斥。弟从以斥之。弟未尝一辞不同于兄。但弟则专就今时某人作何官而言之耳。未尝遽谓义理都不可出也。吾身可以定义理。而义理无定。吾心可以穷义理。而义理无穷。今谓吾身不能如古圣贤。而自弃于义理之外。则不可也。如以吾身已定。吾心已穷。而便谓天下古今之义理。定于此而不可复易。穷于此而不必复究。则斯乃后儒迫塞褊枯之见。而未为古圣贤致广大。尽精微之学也。此弟之所以言言与兄同。而所见则实不能无微异耳。今就兄与我而言。弟则不可出。兄犹在可出不可出之间。弟于他官。决不可出。如今之所叨。则又犹在可出不可出之间。使兄而有此。则弟固不必劝兄以出。兄不出则弟固将为兄喜之。假令兄黾勉一出。弟惟以遄归望兄。必不诮兄以败盟坏节也。非弟之爱兄。不及兄之爱我也。弟之所见义理。正如是故耳。兄则不然。勿论何人何官。惟一出。则视之以万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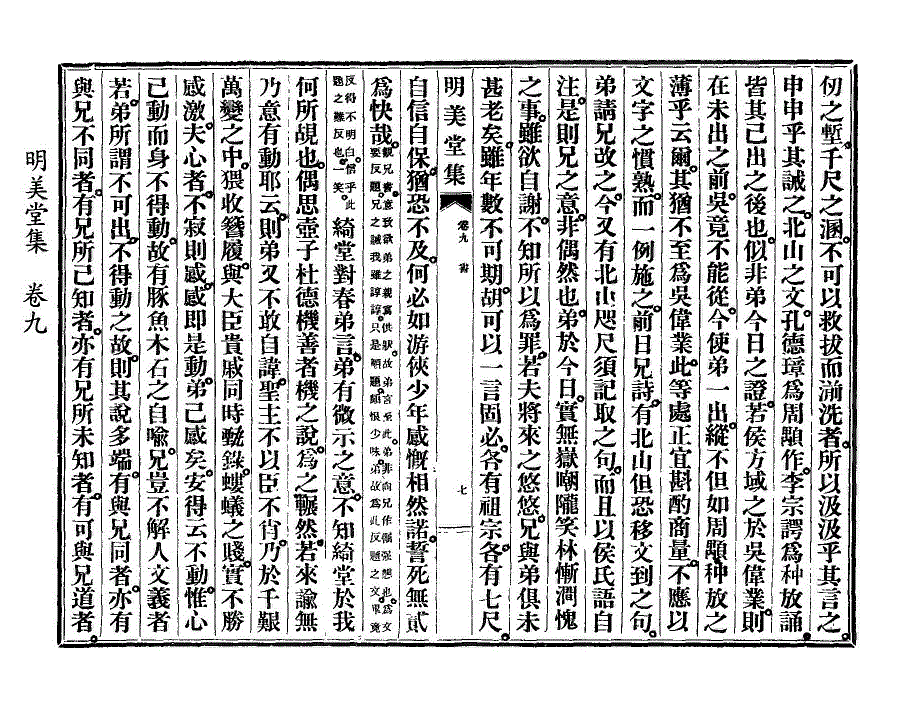 仞之堑。千尺之溷。不可以救拔而湔洗者。所以汲汲乎其言之。申申乎其诫之。北山之文。孔德璋为周颙作。李宗谔为种放诵。皆其已出之后也。似非弟今日之證。若侯方域之于吴伟业。则在未出之前。吴竟不能从。今使弟一出。纵不但如周颙,种放之薄乎云尔。其犹不至为吴伟业。此等处正宜斟酌商量。不应以文字之惯熟。而一例施之。前日兄诗。有北山但恐移文到之句。弟请兄改之。今又有北山咫尺须记取之句。而且以侯氏语自注。是则兄之意。非偶然也。弟于今日。实无岳嘲陇笑林惭涧愧之事。虽欲自谢。不知所以为罪。若夫将来之悠悠。兄与弟俱未甚老矣。虽年数不可期。胡可以一言固必。各有祖宗。各有七尺。自信自保。犹恐不及。何必如游侠少年感慨相然诺。誓死无贰为快哉。(观兄书。意致欲弟之亲写供状。故弟言至此。弟非向兄作倔强态也。为文要反题。兄之诫我虽谆谆。只是顺题。颇恨少味。弟故为此反题之文。毕竟反得不明白。信乎此题之难反也。一笑。)绮堂对春弟言。弟有微示之意。不知绮堂于我何所觇也。偶思壶子杜德机善者机之说。为之冁然。若来谕无乃意有动耶云。则弟又不敢自讳。圣主不以臣不肖。乃于千艰万变之中。猥收簪履。与大臣贵戚同时甄录。蝼蚁之贱。实不胜感激。夫心者。不寂则感。感即是动。弟已感矣。安得云不动。惟心已动而身不得动。故有豚鱼木石之自喻。兄岂不解人文义者若。弟所谓不可出。不得动之故。则其说多端。有与兄同者。亦有与兄不同者。有兄所已知者。亦有兄所未知者。有可与兄道者。
仞之堑。千尺之溷。不可以救拔而湔洗者。所以汲汲乎其言之。申申乎其诫之。北山之文。孔德璋为周颙作。李宗谔为种放诵。皆其已出之后也。似非弟今日之證。若侯方域之于吴伟业。则在未出之前。吴竟不能从。今使弟一出。纵不但如周颙,种放之薄乎云尔。其犹不至为吴伟业。此等处正宜斟酌商量。不应以文字之惯熟。而一例施之。前日兄诗。有北山但恐移文到之句。弟请兄改之。今又有北山咫尺须记取之句。而且以侯氏语自注。是则兄之意。非偶然也。弟于今日。实无岳嘲陇笑林惭涧愧之事。虽欲自谢。不知所以为罪。若夫将来之悠悠。兄与弟俱未甚老矣。虽年数不可期。胡可以一言固必。各有祖宗。各有七尺。自信自保。犹恐不及。何必如游侠少年感慨相然诺。誓死无贰为快哉。(观兄书。意致欲弟之亲写供状。故弟言至此。弟非向兄作倔强态也。为文要反题。兄之诫我虽谆谆。只是顺题。颇恨少味。弟故为此反题之文。毕竟反得不明白。信乎此题之难反也。一笑。)绮堂对春弟言。弟有微示之意。不知绮堂于我何所觇也。偶思壶子杜德机善者机之说。为之冁然。若来谕无乃意有动耶云。则弟又不敢自讳。圣主不以臣不肖。乃于千艰万变之中。猥收簪履。与大臣贵戚同时甄录。蝼蚁之贱。实不胜感激。夫心者。不寂则感。感即是动。弟已感矣。安得云不动。惟心已动而身不得动。故有豚鱼木石之自喻。兄岂不解人文义者若。弟所谓不可出。不得动之故。则其说多端。有与兄同者。亦有与兄不同者。有兄所已知者。亦有兄所未知者。有可与兄道者。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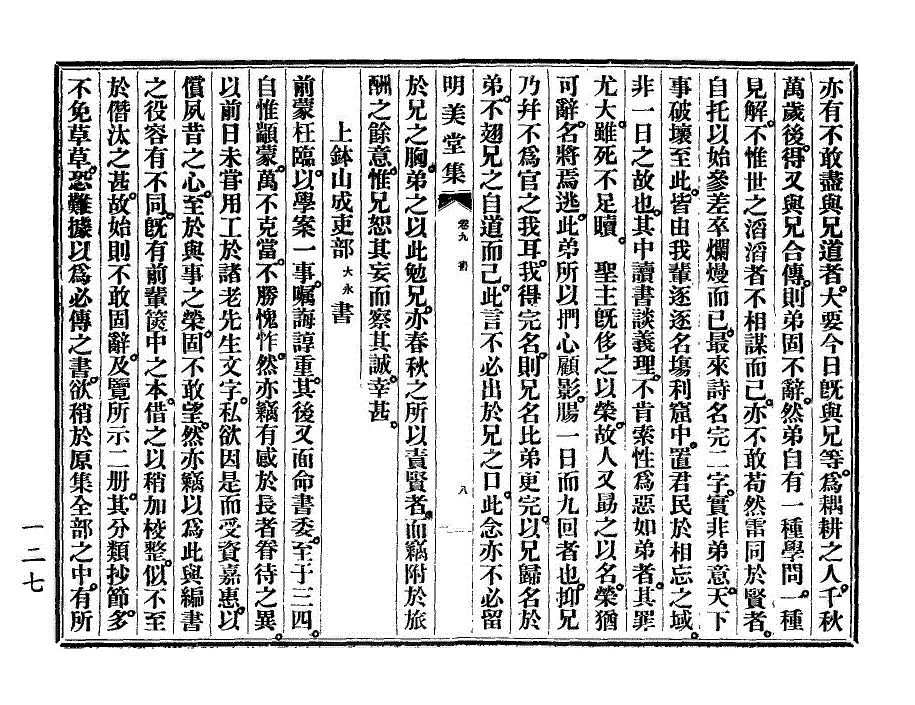 亦有不敢尽与兄道者。大要今日既与兄等。为耦耕之人。千秋万岁后。得又与兄合传。则弟固不辞。然弟自有一种学问。一种见解。不惟世之滔滔者不相谋而已。亦不敢苟然雷同于贤者。自托以始参差卒烂熳而已。最来诗名完二字。实非弟意。天下事破坏至此。皆由我辈逐逐名场利窟中。置君民于相忘之域。非一日之故也。其中读书谈义理。不肯索性为恶如弟者。其罪尤大。虽死不足赎。 圣主既侈之以荣。故人又勖之以名。荣犹可辞。名将焉逃。此弟所以扪心顾影。肠一日而九回者也。抑兄乃并不为官之我耳。我得完名。则兄名比弟更完。以兄归名于弟。不翅兄之自道而已。此言不必出于兄之口。此念亦不必留于兄之胸。弟之以此勉兄。亦春秋之所以责贤者。而窃附于旅酬之馀意。惟兄恕其妄而察其诚。幸甚。
亦有不敢尽与兄道者。大要今日既与兄等。为耦耕之人。千秋万岁后。得又与兄合传。则弟固不辞。然弟自有一种学问。一种见解。不惟世之滔滔者不相谋而已。亦不敢苟然雷同于贤者。自托以始参差卒烂熳而已。最来诗名完二字。实非弟意。天下事破坏至此。皆由我辈逐逐名场利窟中。置君民于相忘之域。非一日之故也。其中读书谈义理。不肯索性为恶如弟者。其罪尤大。虽死不足赎。 圣主既侈之以荣。故人又勖之以名。荣犹可辞。名将焉逃。此弟所以扪心顾影。肠一日而九回者也。抑兄乃并不为官之我耳。我得完名。则兄名比弟更完。以兄归名于弟。不翅兄之自道而已。此言不必出于兄之口。此念亦不必留于兄之胸。弟之以此勉兄。亦春秋之所以责贤者。而窃附于旅酬之馀意。惟兄恕其妄而察其诚。幸甚。上钵山成吏部(大永)书
前蒙枉临。以学案一事。嘱诲谆重。其后又面命书委。至于三四。自惟颛蒙。万不克当。不胜愧怍。然亦窃有感于长者眷待之异。以前日未尝用工于诸老先生文字。私欲因是而受资嘉惠。以偿夙昔之心。至于与事之荣。固不敢望。然亦窃以为此与编书之役容有不同。既有前辈箧中之本。借之以稍加校整。似不至于僭汰之甚。故始则不敢固辞。及览所示二册。其分类抄节。多不免草草。恐难据以为必传之书。欲稍于原集全部之中。有所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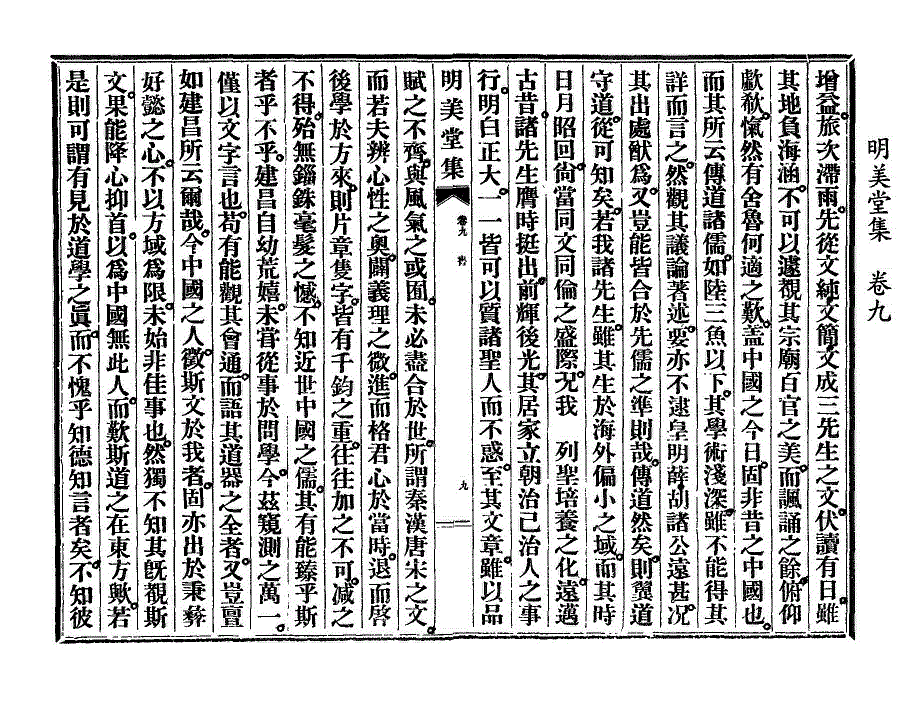 增益。旅次滞雨。先从文纯,文简,文成三先生之文。伏读有日。虽其地负海涵。不可以遽睹其宗庙百官之美。而讽诵之馀。俯仰歔欷。忾然有舍鲁何适之叹。盖中国之今日。固非昔之中国也。而其所云传道诸儒。如陆三鱼以下。其学术浅深。虽不能得其详而言之。然观其议论著述。要亦不逮皇明薛,胡诸公远甚。况其出处猷为。又岂能皆合于先儒之准则哉。传道然矣。则翼道守道。从可知矣。若我诸先生。虽其生于海外偏小之域。而其时日月昭回。尚当同文同伦之盛际。况我 列圣培养之化。远迈古昔。诸先生膺时挺出。前辉后光。其居家立朝治己治人之事行。明白正大。一一皆可以质诸圣人而不惑。至其文章。虽以品赋之不齐。与风气之或囿。未必尽合于世。所谓秦汉唐宋之文。而若夫辨心性之奥。辟义理之微。进而格君心于当时。退而启后学于方来。则片章只字。皆有千钧之重。往往加之不可。减之不得。殆无锱铢毫发之憾。不知近世中国之儒。其有能臻乎斯者乎不乎。建昌自幼荒嬉。未尝从事于问学。今兹窥测之万一。仅以文字言也。苟有能观其会通。而语其道器之全者。又岂亶如建昌所云尔哉。今中国之人。徵斯文于我者。固亦出于秉彝好懿之心。不以方域为限。未始非佳事也。然独不知其既睹斯文。果能降心抑首。以为中国无此人。而叹斯道之在东方欤。若是则可谓有见于道学之真。而不愧乎知德知言者矣。不知彼
增益。旅次滞雨。先从文纯,文简,文成三先生之文。伏读有日。虽其地负海涵。不可以遽睹其宗庙百官之美。而讽诵之馀。俯仰歔欷。忾然有舍鲁何适之叹。盖中国之今日。固非昔之中国也。而其所云传道诸儒。如陆三鱼以下。其学术浅深。虽不能得其详而言之。然观其议论著述。要亦不逮皇明薛,胡诸公远甚。况其出处猷为。又岂能皆合于先儒之准则哉。传道然矣。则翼道守道。从可知矣。若我诸先生。虽其生于海外偏小之域。而其时日月昭回。尚当同文同伦之盛际。况我 列圣培养之化。远迈古昔。诸先生膺时挺出。前辉后光。其居家立朝治己治人之事行。明白正大。一一皆可以质诸圣人而不惑。至其文章。虽以品赋之不齐。与风气之或囿。未必尽合于世。所谓秦汉唐宋之文。而若夫辨心性之奥。辟义理之微。进而格君心于当时。退而启后学于方来。则片章只字。皆有千钧之重。往往加之不可。减之不得。殆无锱铢毫发之憾。不知近世中国之儒。其有能臻乎斯者乎不乎。建昌自幼荒嬉。未尝从事于问学。今兹窥测之万一。仅以文字言也。苟有能观其会通。而语其道器之全者。又岂亶如建昌所云尔哉。今中国之人。徵斯文于我者。固亦出于秉彝好懿之心。不以方域为限。未始非佳事也。然独不知其既睹斯文。果能降心抑首。以为中国无此人。而叹斯道之在东方欤。若是则可谓有见于道学之真。而不愧乎知德知言者矣。不知彼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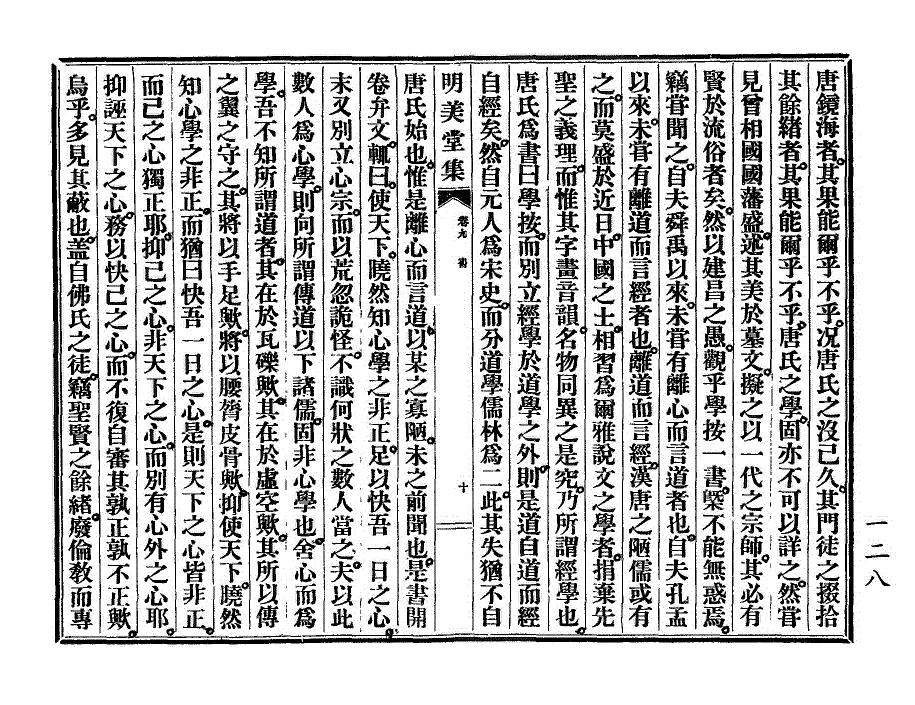 唐镜海者。其果能尔乎不乎。况唐氏之没已久。其门徒之掇拾其馀绪者。其果能尔乎不乎。唐氏之学。固亦不可以详之。然尝见曾相国国藩盛。述其美于墓文。拟之以一代之宗师。其必有贤于流俗者矣。然以建昌之愚。观乎学按一书。槩不能无惑焉。窃尝闻之。自夫舜禹以来。未尝有离心而言道者也。自夫孔孟以来。未尝有离道而言经者也。离道而言经。汉唐之陋儒或有之。而莫盛于近日。中国之士。相习为尔雅说文之学者。捐弃先圣之义理。而惟其字画音韵。名物同异之是究。乃所谓经学也。唐氏为书曰学按。而别立经学于道学之外。则是道自道而经自经矣。然自元人为宋史。而分道学儒林为二。此其失犹不自唐氏始也。惟是离心而言道。以某之寡陋。未之前闻也。是书开卷弁文。辄曰。使天下。晓然知心学之非正。足以快吾一日之心。末又别立心宗。而以荒忽诡怪。不识何状之数人当之。夫以此数人为心学。则向所谓传道以下诸儒。固非心学也。舍心而为学。吾不知所谓道者。其在于瓦砾欤。其在于虚空欤。其所以传之翼之守之。其将以手足欤。将以腰膂皮骨欤。抑使天下。晓然知心学之非正。而犹曰快吾一日之心。是则天下之心皆非正。而己之心独正耶。抑己之心。非天下之心。而别有心外之心耶。抑诬天下之心。务以快己之心。而不复自审其孰正孰不正欤。乌乎。多见其蔽也。盖自佛氏之徒。窃圣贤之馀绪。废伦教而专
唐镜海者。其果能尔乎不乎。况唐氏之没已久。其门徒之掇拾其馀绪者。其果能尔乎不乎。唐氏之学。固亦不可以详之。然尝见曾相国国藩盛。述其美于墓文。拟之以一代之宗师。其必有贤于流俗者矣。然以建昌之愚。观乎学按一书。槩不能无惑焉。窃尝闻之。自夫舜禹以来。未尝有离心而言道者也。自夫孔孟以来。未尝有离道而言经者也。离道而言经。汉唐之陋儒或有之。而莫盛于近日。中国之士。相习为尔雅说文之学者。捐弃先圣之义理。而惟其字画音韵。名物同异之是究。乃所谓经学也。唐氏为书曰学按。而别立经学于道学之外。则是道自道而经自经矣。然自元人为宋史。而分道学儒林为二。此其失犹不自唐氏始也。惟是离心而言道。以某之寡陋。未之前闻也。是书开卷弁文。辄曰。使天下。晓然知心学之非正。足以快吾一日之心。末又别立心宗。而以荒忽诡怪。不识何状之数人当之。夫以此数人为心学。则向所谓传道以下诸儒。固非心学也。舍心而为学。吾不知所谓道者。其在于瓦砾欤。其在于虚空欤。其所以传之翼之守之。其将以手足欤。将以腰膂皮骨欤。抑使天下。晓然知心学之非正。而犹曰快吾一日之心。是则天下之心皆非正。而己之心独正耶。抑己之心。非天下之心。而别有心外之心耶。抑诬天下之心。务以快己之心。而不复自审其孰正孰不正欤。乌乎。多见其蔽也。盖自佛氏之徒。窃圣贤之馀绪。废伦教而专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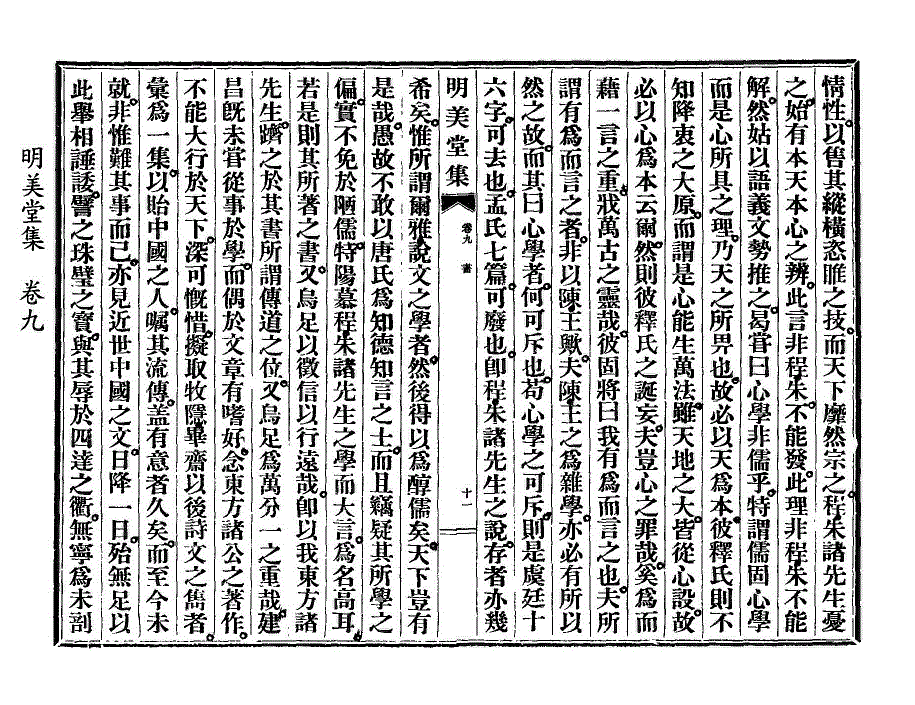 情性。以售其纵横恣睢之技。而天下靡然宗之。程,朱诸先生忧之。始有本天本心之辨。此言非程,朱。不能发。此理非程,朱不能解。然姑以语义文势推之。曷尝曰心学非儒乎。特谓儒固心学而是心所具之理。乃天之所畀也。故必以天为本。彼释氏则不知降衷之大原。而谓是心能生万法。虽天地之大。皆从心设。故必以心为本云尔。然则彼释氏之诞妄。夫岂心之罪哉。奚为而藉一言之重。戕万古之灵哉。彼固将曰我有为而言之也。夫所谓有为而言之者。非以陈,王欤。夫陈,王之为杂学。亦必有所以然之故。而其曰心学者。何可斥也。苟心学之可斥。则是虞廷十六字。可去也。孟氏七篇。可废也。即程,朱诸先生之说。存者亦几希矣。惟所谓尔雅,说文之学者。然后得以为醇儒矣。天下岂有是哉。愚故不敢以唐氏为知德知言之士。而且窃疑其所学之偏。实不免于陋儒。特阳慕程,朱诸先生之学而大言。为名高耳。若是则其所著之书。又乌足以徵信以行远哉。即以我东方诸先生。跻之于其书所谓传道之位。又乌足为万分一之重哉。建昌既未尝从事于学。而偶于文章有嗜好。念东方诸公之著作。不能大行于天下。深可慨惜。拟取牧隐,毕斋以后诗文之隽者。汇为一集。以贻中国之人。嘱其流传。盖有意者久矣。而至今未就。非惟难其事而已。亦见近世中国之文。日降一日。殆无足以此举相諈诿。譬之珠璧之宝。与其辱于四达之衢。无宁为未剖
情性。以售其纵横恣睢之技。而天下靡然宗之。程,朱诸先生忧之。始有本天本心之辨。此言非程,朱。不能发。此理非程,朱不能解。然姑以语义文势推之。曷尝曰心学非儒乎。特谓儒固心学而是心所具之理。乃天之所畀也。故必以天为本。彼释氏则不知降衷之大原。而谓是心能生万法。虽天地之大。皆从心设。故必以心为本云尔。然则彼释氏之诞妄。夫岂心之罪哉。奚为而藉一言之重。戕万古之灵哉。彼固将曰我有为而言之也。夫所谓有为而言之者。非以陈,王欤。夫陈,王之为杂学。亦必有所以然之故。而其曰心学者。何可斥也。苟心学之可斥。则是虞廷十六字。可去也。孟氏七篇。可废也。即程,朱诸先生之说。存者亦几希矣。惟所谓尔雅,说文之学者。然后得以为醇儒矣。天下岂有是哉。愚故不敢以唐氏为知德知言之士。而且窃疑其所学之偏。实不免于陋儒。特阳慕程,朱诸先生之学而大言。为名高耳。若是则其所著之书。又乌足以徵信以行远哉。即以我东方诸先生。跻之于其书所谓传道之位。又乌足为万分一之重哉。建昌既未尝从事于学。而偶于文章有嗜好。念东方诸公之著作。不能大行于天下。深可慨惜。拟取牧隐,毕斋以后诗文之隽者。汇为一集。以贻中国之人。嘱其流传。盖有意者久矣。而至今未就。非惟难其事而已。亦见近世中国之文。日降一日。殆无足以此举相諈诿。譬之珠璧之宝。与其辱于四达之衢。无宁为未剖明美堂集卷九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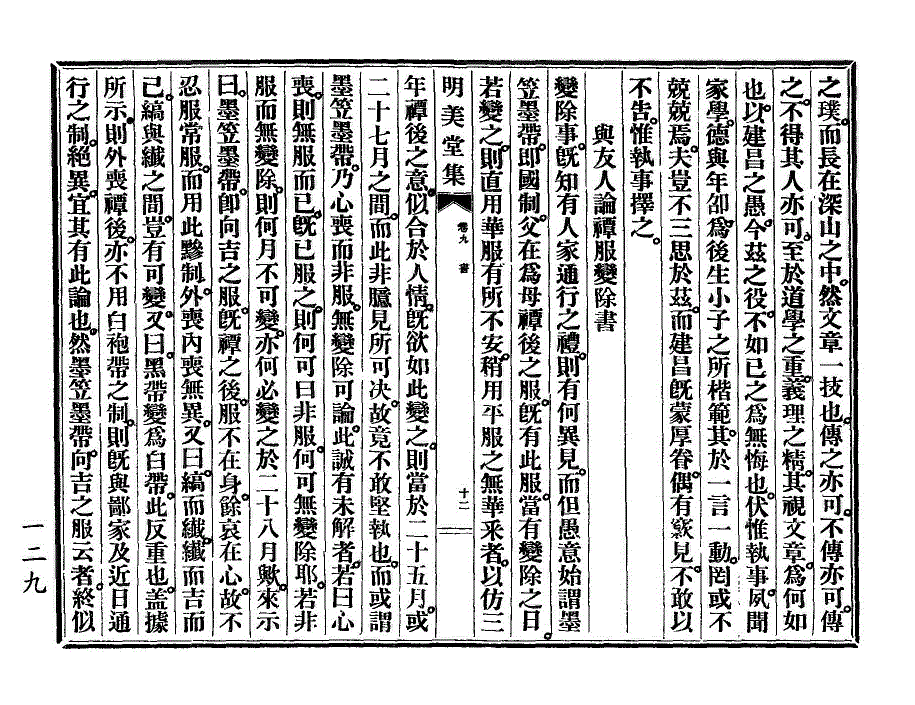 之璞。而长在深山之中。然文章一技也。传之亦可。不传亦可。传之。不得其人亦可。至于道学之重。义理之精。其视文章。为何如也。以建昌之愚。今兹之役。不如已之为无悔也。伏惟执事。夙闻家学。德与年卲。为后生小子之所楷范。其于一言一动。罔或不兢兢焉。夫岂不三思于兹。而建昌既蒙厚眷。偶有窾见。不敢以不告。惟执事择之。
之璞。而长在深山之中。然文章一技也。传之亦可。不传亦可。传之。不得其人亦可。至于道学之重。义理之精。其视文章。为何如也。以建昌之愚。今兹之役。不如已之为无悔也。伏惟执事。夙闻家学。德与年卲。为后生小子之所楷范。其于一言一动。罔或不兢兢焉。夫岂不三思于兹。而建昌既蒙厚眷。偶有窾见。不敢以不告。惟执事择之。与友人论禫服变除书
变除事。既知有人家通行之礼。则有何异见。而但愚意始谓墨笠墨带。即国制。父在为母禫后之服。既有此服。当有变除之日。若变之。则直用华服有所不安。稍用平服之无华采者。以仿三年禫后之意。似合于人情。既欲如此变之。则当于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之间。而此非臆见所可决。故竟不敢坚执也。而或谓墨笠墨带。乃心丧而非服。无变除可论。此诚有未解者。若曰心丧。则无服而已。既已服之。则何可曰非服。何可无变除耶。若非服而无变除。则何月不可变。亦何必变之于二十八月欤。来示曰。墨笠墨带。即向吉之服。既禫之后。服不在身。馀哀在心。故不忍服常服。而用此黪制。外丧内丧无异。又曰。缟而纤。纤而吉而已。缟与纤之间。岂有可变。又曰。黑带变为白带。此反重也。盖据所示。则外丧禫后。亦不用白袍带之制。则既与鄙家及近日通行之制。绝异。宜其有此论也。然墨笠墨带。向吉之服云者。终似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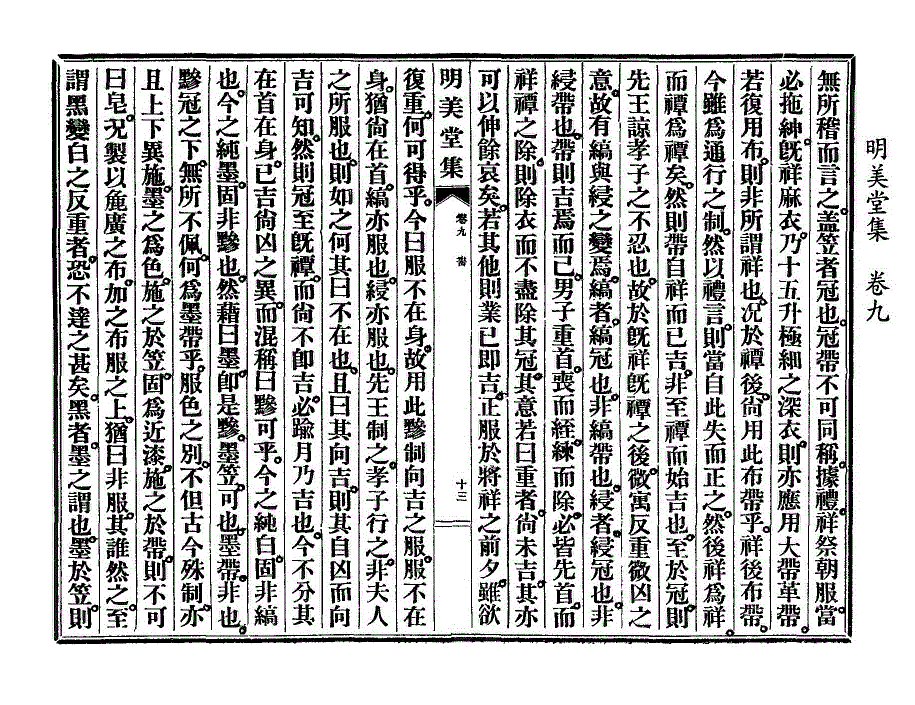 无所稽而言之。盖笠者冠也。冠带不可同称。据礼。祥祭朝服。当必拖绅。既祥麻衣。乃十五升极细之深衣。则亦应用大带革带。若复用布。则非所谓祥也。况于禫后。尚用此布带乎。祥后布带。今虽为通行之制。然以礼言。则当自此失而正之。然后祥为祥。而禫为禫矣。然则带自祥而已吉。非至禫而始吉也。至于冠。则先王谅孝子之不忍也。故于既祥既禫之后。微寓反重微凶之意。故有缟与綅之变焉。缟者。缟冠也。非缟带也。綅者。綅冠也。非綅带也。带则吉焉而已。男子重首。丧而绖。练而除。必皆先首。而祥禫之除。则除衣而不尽除其冠。其意若曰重者。尚未吉。其亦可以伸馀哀矣。若其他则业已即吉。正服于将祥之前夕。虽欲复重。何可得乎。今曰服不在身。故用此黪制向吉之服。服不在身。犹尚在首。缟亦服也。綅亦服也。先王制之。孝子行之。非夫人之所服也。则如之何其曰不在也。且曰其向吉。则其自凶而向吉可知。然则冠至既禫。而尚不即吉。必踰月乃吉也。今不分其在首在身。已吉尚凶之异。而混称曰黪可乎。今之纯白。固非缟也。今之纯墨。固非黪也。然藉曰墨。即是黪。墨笠。可也。墨带。非也。黪冠之下。无所不佩。何为墨带乎。服色之别。不但古今殊制。亦且上下异施。墨之为色。施之于笠。固为近漆。施之于带。则不可曰皂。况制以粗广之布。加之布服之上。犹曰非服。其谁然之。至谓黑变白之反重者。恐不达之甚矣。黑者。墨之谓也。墨于笠。则
无所稽而言之。盖笠者冠也。冠带不可同称。据礼。祥祭朝服。当必拖绅。既祥麻衣。乃十五升极细之深衣。则亦应用大带革带。若复用布。则非所谓祥也。况于禫后。尚用此布带乎。祥后布带。今虽为通行之制。然以礼言。则当自此失而正之。然后祥为祥。而禫为禫矣。然则带自祥而已吉。非至禫而始吉也。至于冠。则先王谅孝子之不忍也。故于既祥既禫之后。微寓反重微凶之意。故有缟与綅之变焉。缟者。缟冠也。非缟带也。綅者。綅冠也。非綅带也。带则吉焉而已。男子重首。丧而绖。练而除。必皆先首。而祥禫之除。则除衣而不尽除其冠。其意若曰重者。尚未吉。其亦可以伸馀哀矣。若其他则业已即吉。正服于将祥之前夕。虽欲复重。何可得乎。今曰服不在身。故用此黪制向吉之服。服不在身。犹尚在首。缟亦服也。綅亦服也。先王制之。孝子行之。非夫人之所服也。则如之何其曰不在也。且曰其向吉。则其自凶而向吉可知。然则冠至既禫。而尚不即吉。必踰月乃吉也。今不分其在首在身。已吉尚凶之异。而混称曰黪可乎。今之纯白。固非缟也。今之纯墨。固非黪也。然藉曰墨。即是黪。墨笠。可也。墨带。非也。黪冠之下。无所不佩。何为墨带乎。服色之别。不但古今殊制。亦且上下异施。墨之为色。施之于笠。固为近漆。施之于带。则不可曰皂。况制以粗广之布。加之布服之上。犹曰非服。其谁然之。至谓黑变白之反重者。恐不达之甚矣。黑者。墨之谓也。墨于笠。则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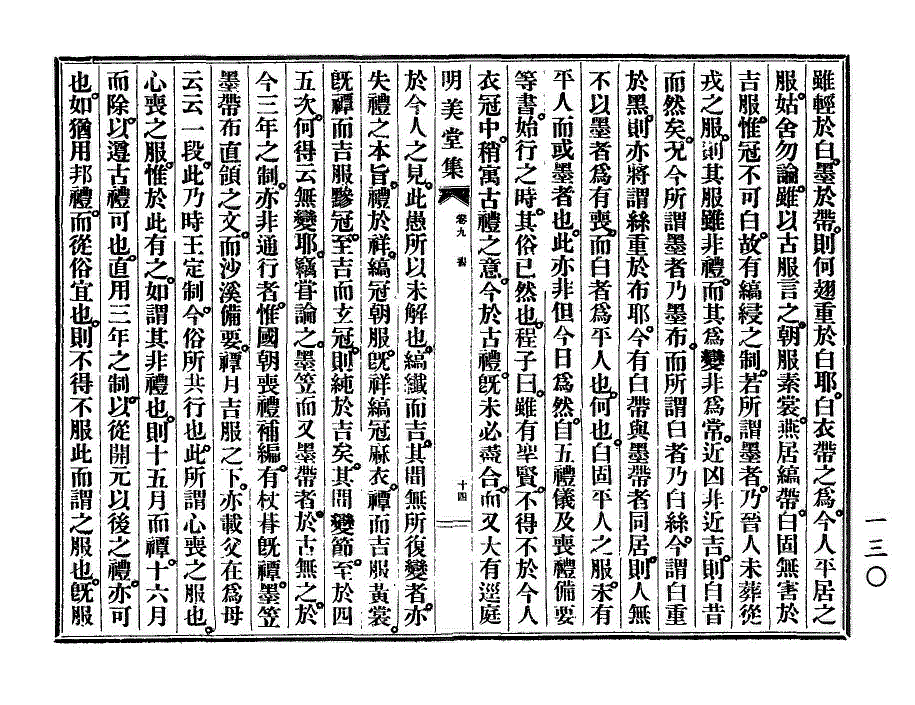 虽轻于白。墨于带。则何翅重于白耶。白衣带之为。今人平居之服。姑舍勿论。虽以古服言之。朝服素裳。燕居缟带。白固无害于吉服。惟冠不可白。故有缟綅之制。若所谓墨者。乃晋人未葬从戎之服。则其服虽非礼。而其为变非为常。近凶非近吉。则自昔而然矣。况今所谓墨者乃墨布。而所谓白者乃白丝。今谓白重于黑。则亦将谓丝重于布耶。今有白带与墨带者同居。则人无不以墨者为有丧。而白者为平人也。何也。白固平人之服。未有平人而或墨者也。此亦非但今日为然。自五礼仪及丧礼备要等书。始行之时。其俗已然也。程子曰。虽有圣贤。不得不于今人衣冠中。稍寓古礼之意。今于古礼。既未必尽合。而又大有径庭于今人之见。此愚所以未解也。缟纤而吉。其间无所复变者。亦失礼之本旨。礼于祥。缟冠朝服。既祥缟冠麻衣。禫而吉服黄裳。既禫而吉服黪冠。至吉而玄冠。则纯于吉矣。其间变节。至于四五次。何得云无变耶。窃尝论之。墨笠而又墨带者。于古无之。于今三年之制。亦非通行者。惟国朝丧礼补编。有杖期既禫。墨笠墨带布直领之文。而沙溪备要。禫月吉服之下。亦载父在为母云云一段。此乃时王定制。今俗所共行也。此所谓心丧之服也。心丧之服。惟于此有之。如谓其非礼也。则十五月而禫。十六月而除。以遵古礼可也。直用三年之制。以从开元以后之礼。亦可也。如犹用邦礼。而从俗宜也。则不得不服此而谓之服也。既服
虽轻于白。墨于带。则何翅重于白耶。白衣带之为。今人平居之服。姑舍勿论。虽以古服言之。朝服素裳。燕居缟带。白固无害于吉服。惟冠不可白。故有缟綅之制。若所谓墨者。乃晋人未葬从戎之服。则其服虽非礼。而其为变非为常。近凶非近吉。则自昔而然矣。况今所谓墨者乃墨布。而所谓白者乃白丝。今谓白重于黑。则亦将谓丝重于布耶。今有白带与墨带者同居。则人无不以墨者为有丧。而白者为平人也。何也。白固平人之服。未有平人而或墨者也。此亦非但今日为然。自五礼仪及丧礼备要等书。始行之时。其俗已然也。程子曰。虽有圣贤。不得不于今人衣冠中。稍寓古礼之意。今于古礼。既未必尽合。而又大有径庭于今人之见。此愚所以未解也。缟纤而吉。其间无所复变者。亦失礼之本旨。礼于祥。缟冠朝服。既祥缟冠麻衣。禫而吉服黄裳。既禫而吉服黪冠。至吉而玄冠。则纯于吉矣。其间变节。至于四五次。何得云无变耶。窃尝论之。墨笠而又墨带者。于古无之。于今三年之制。亦非通行者。惟国朝丧礼补编。有杖期既禫。墨笠墨带布直领之文。而沙溪备要。禫月吉服之下。亦载父在为母云云一段。此乃时王定制。今俗所共行也。此所谓心丧之服也。心丧之服。惟于此有之。如谓其非礼也。则十五月而禫。十六月而除。以遵古礼可也。直用三年之制。以从开元以后之礼。亦可也。如犹用邦礼。而从俗宜也。则不得不服此而谓之服也。既服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1H 页
 此而谓之服。则不得不有时而除之。谓之除服也。夫以礼而言。则三年既禫之服。亦失于厚。(不从吉)以情而言。则杖期既禫之服。犹恨其轻。(为尊所压)然厚亦服也。轻亦服也。谓之非所当服则可。谓之非服则不可。谓之当变不变。不当变而变。则可。谓之无可变。则不可矣。(朱子家礼。大祥直陈禫服。有黪而无缟。此后儒所疑。而朱子亦自言家礼未成书者也。今以墨笠墨带。合之曰黪者。盖昉于家礼。然家礼。亦无黪带之文。只称黪衫布带。黪衫。今无用之者。亦无于大祥不着白笠而直着墨笠者。然则家礼之不合于今俗也。明矣。)
此而谓之服。则不得不有时而除之。谓之除服也。夫以礼而言。则三年既禫之服。亦失于厚。(不从吉)以情而言。则杖期既禫之服。犹恨其轻。(为尊所压)然厚亦服也。轻亦服也。谓之非所当服则可。谓之非服则不可。谓之当变不变。不当变而变。则可。谓之无可变。则不可矣。(朱子家礼。大祥直陈禫服。有黪而无缟。此后儒所疑。而朱子亦自言家礼未成书者也。今以墨笠墨带。合之曰黪者。盖昉于家礼。然家礼。亦无黪带之文。只称黪衫布带。黪衫。今无用之者。亦无于大祥不着白笠而直着墨笠者。然则家礼之不合于今俗也。明矣。)明美堂集卷九(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序
送湖南伯石汀郑公(范朝)序
曩余闻湖南之胜而乐之。其山水清而夷。其土上壤。农桑之利倍焉。嘉鱼登于川泽。而橘柚竹林之植。葱茜映翳。可比屋而望也。环一国之内。上自卿大夫。下至庶人。凡婚姻祭祀日用服食之所须。过半出湖南。而湖南之人不少损。岂所谓乐土者。非欤。然其民好末技而健讼。其吏胥。老于奸。号难治。其士寥寥然百年。鲜以孝秀明经著者。将富厚之佚人。而怠于义欤。抑上之人导之或未善欤。何其地之美如此。而风俗有不及也。日者。朝廷命直学士郑公涖湖南。公故相经山公之孙。而今尚书公之胤子。由词学清华进。荐长馆阁。 人主方向公甚殷。不欲一日处于外。而特以是畀之。此湖南得公。而非公得湖南也。然余区区独私贺于公者。以湖南之乐名国中。吾侪耳之已久。而仕宦于京都。相去半千里。何由膏车秣马而从之。即令地近可居。亦不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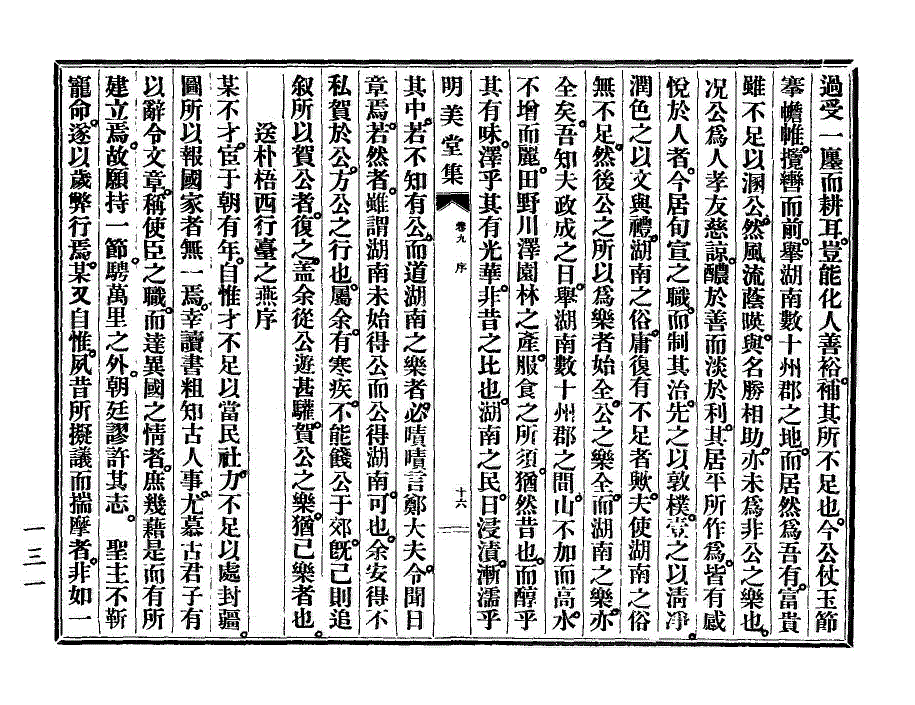 过受一廛而耕耳。岂能化人善裕。补其所不足也。今公仗玉节搴幨帷。揽辔而前。举湖南数十州郡之地。而居然为吾有。富贵虽不足以溷公。然风流荫映。与名胜相助。亦未为非公之乐也。况公为人孝友慈谅。醲于善而淡于利。其居平所作为。皆有感悦于人者。今居旬宣之职。而制其治。先之以敦朴。壹之以清净。润色之以文与礼。湖南之俗。庸复有不足者欤。夫使湖南之俗无不足。然后公之所以为乐者始全。公之乐全。而湖南之乐。亦全矣。吾知夫政成之日。举湖南数十州郡之间。山不加而高。水不增而丽。田野川泽园林之产。服食之所须。犹然昔也。而醇乎其有味。泽乎其有光华。非昔之比也。湖南之民。日浸渍。渐濡乎其中。若不知有公。而道湖南之乐者。必啧啧言郑大夫。令闻日章焉。若然者。虽谓湖南未始得公而公得湖南。可也。余安得不私贺于公。方公之行也。属余。有寒疾。不能饯公于郊。既已则追叙所以贺公者。复之。盖余从公游甚驩。贺公之乐。犹己乐者也。
过受一廛而耕耳。岂能化人善裕。补其所不足也。今公仗玉节搴幨帷。揽辔而前。举湖南数十州郡之地。而居然为吾有。富贵虽不足以溷公。然风流荫映。与名胜相助。亦未为非公之乐也。况公为人孝友慈谅。醲于善而淡于利。其居平所作为。皆有感悦于人者。今居旬宣之职。而制其治。先之以敦朴。壹之以清净。润色之以文与礼。湖南之俗。庸复有不足者欤。夫使湖南之俗无不足。然后公之所以为乐者始全。公之乐全。而湖南之乐。亦全矣。吾知夫政成之日。举湖南数十州郡之间。山不加而高。水不增而丽。田野川泽园林之产。服食之所须。犹然昔也。而醇乎其有味。泽乎其有光华。非昔之比也。湖南之民。日浸渍。渐濡乎其中。若不知有公。而道湖南之乐者。必啧啧言郑大夫。令闻日章焉。若然者。虽谓湖南未始得公而公得湖南。可也。余安得不私贺于公。方公之行也。属余。有寒疾。不能饯公于郊。既已则追叙所以贺公者。复之。盖余从公游甚驩。贺公之乐。犹己乐者也。送朴梧西行台之燕序
某不才。宦于朝有年。自惟才不足以当民社。力不足以处封疆。图所以报国家者无一焉。幸读书粗知古人事。尤慕古君子有以辞令文章。称使臣之职。而达异国之情者。庶几藉是而有所建立焉。故愿持一节。骋万里之外。朝廷谬许其志。 圣主不靳宠命。遂以岁弊行焉。某又自惟。夙昔所拟议而揣摩者。非如一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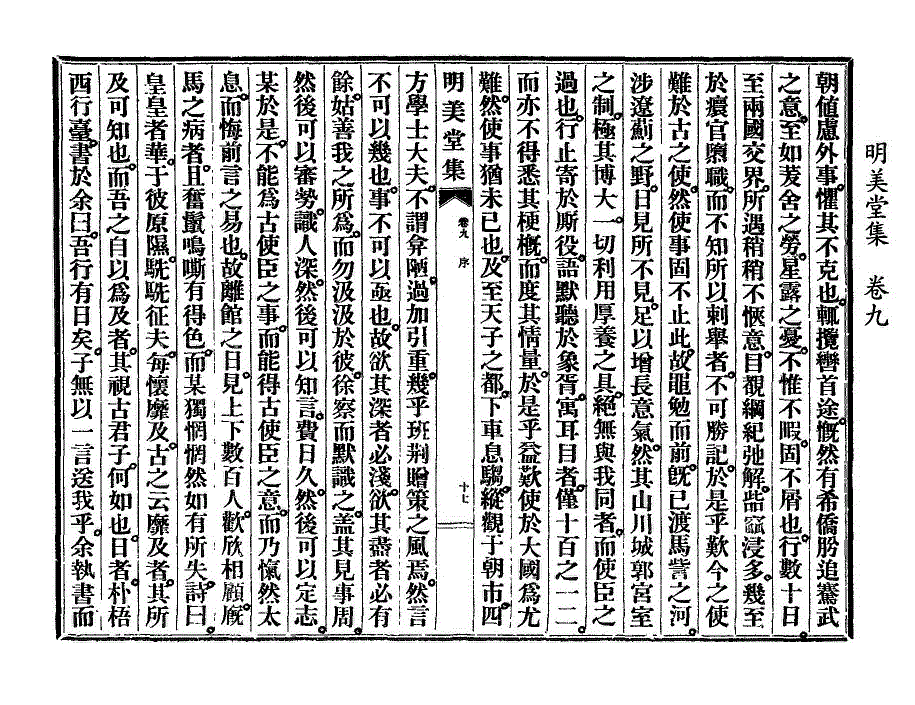 朝值虑外事。惧其不克也。辄揽辔首途。慨然有希侨肸追骞武之意。至如茇舍之劳。星露之忧。不惟不暇。固不屑也。行数十日。至两国交界。所遇稍稍不惬意。目睹纲纪弛解。啙窳浸多。几至于瘝官隳职。而不知所以刺举者。不可胜记。于是乎叹今之使难于古之使。然使事固不止此。故黾勉而前。既已渡马訾之河。涉辽蓟之野。日见所不见。足以增长意气。然其山川城郭宫室之制。极其博大。一切利用厚养之具。绝无与我同者。而使臣之过也。行止寄于厮役。语默听于象胥。寓耳目者。仅十百之一二。而亦不得悉其梗概。而度其情量。于是乎益叹使于大国为尤难。然使事犹未已也。及至天子之都。下车息驺。纵观于朝市。四方学士大夫。不谓弇陋。过加引重。几乎班荆赠策之风焉。然言不可以几也。事不可以亟也。故欲其深者必浅。欲其尽者必有馀。姑善我之所为。而勿汲汲于彼。徐察而默识之。盖其见事周。然后可以审势。识人深。然后可以知言。费日久。然后可以定志。某于是。不能为古使臣之事。而能得古使臣之意。而乃忾然太息。而悔前言之易也。故离馆之日。见士下数百人。欢欣相顾。厩马之病者。且奋鬣鸣嘶有得色。而某独惘惘然如有所失。诗曰。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古之云靡及者。其所及可知也。而吾之自以为及者。其视古君子。何如也。日者。朴梧西行台。书于余曰。吾行有日矣。子无以一言送我乎。余执书而
朝值虑外事。惧其不克也。辄揽辔首途。慨然有希侨肸追骞武之意。至如茇舍之劳。星露之忧。不惟不暇。固不屑也。行数十日。至两国交界。所遇稍稍不惬意。目睹纲纪弛解。啙窳浸多。几至于瘝官隳职。而不知所以刺举者。不可胜记。于是乎叹今之使难于古之使。然使事固不止此。故黾勉而前。既已渡马訾之河。涉辽蓟之野。日见所不见。足以增长意气。然其山川城郭宫室之制。极其博大。一切利用厚养之具。绝无与我同者。而使臣之过也。行止寄于厮役。语默听于象胥。寓耳目者。仅十百之一二。而亦不得悉其梗概。而度其情量。于是乎益叹使于大国为尤难。然使事犹未已也。及至天子之都。下车息驺。纵观于朝市。四方学士大夫。不谓弇陋。过加引重。几乎班荆赠策之风焉。然言不可以几也。事不可以亟也。故欲其深者必浅。欲其尽者必有馀。姑善我之所为。而勿汲汲于彼。徐察而默识之。盖其见事周。然后可以审势。识人深。然后可以知言。费日久。然后可以定志。某于是。不能为古使臣之事。而能得古使臣之意。而乃忾然太息。而悔前言之易也。故离馆之日。见士下数百人。欢欣相顾。厩马之病者。且奋鬣鸣嘶有得色。而某独惘惘然如有所失。诗曰。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古之云靡及者。其所及可知也。而吾之自以为及者。其视古君子。何如也。日者。朴梧西行台。书于余曰。吾行有日矣。子无以一言送我乎。余执书而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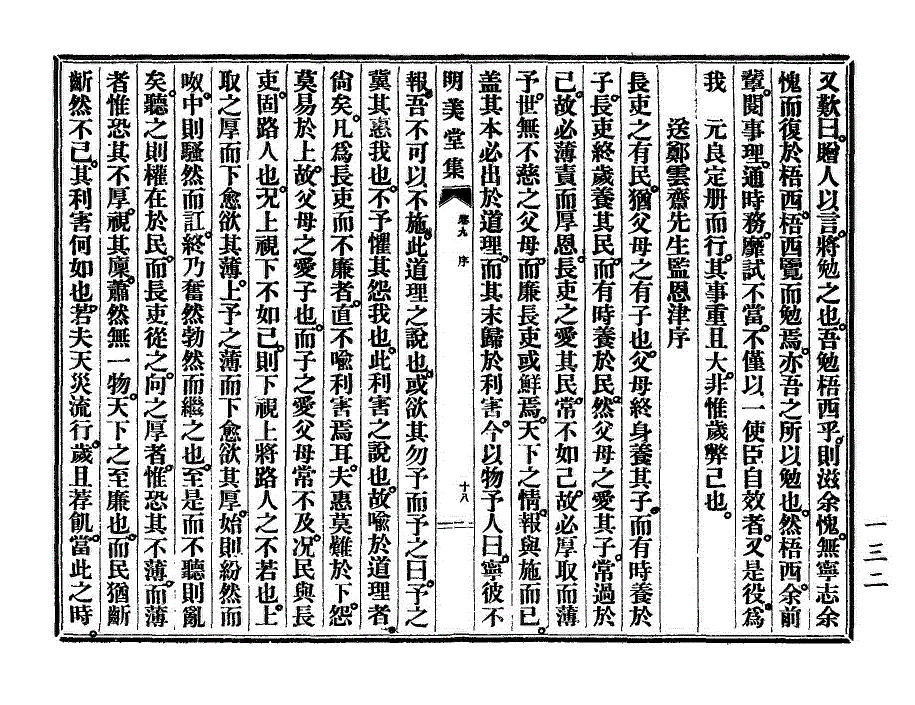 又叹曰。赠人以言。将勉之也。吾勉梧西乎。则滋余愧。无宁志余愧而复于梧西。梧西览而勉焉。亦吾之所以勉也。然梧西。余前辈。阅事理。通时务。靡试不当。不仅以一使臣自效者。又是役。为我 元良定册而行。其事重且大。非惟岁弊已也。
又叹曰。赠人以言。将勉之也。吾勉梧西乎。则滋余愧。无宁志余愧而复于梧西。梧西览而勉焉。亦吾之所以勉也。然梧西。余前辈。阅事理。通时务。靡试不当。不仅以一使臣自效者。又是役。为我 元良定册而行。其事重且大。非惟岁弊已也。送郑云斋先生监恩津序
长吏之有民。犹父母之有子也。父母终身养其子。而有时养于子。长吏终岁养其民。而有时养于民。然父母之爱其子。常过于己。故必薄责而厚恩。长吏之爱其民。常不如己。故必厚取而薄予。世无不慈之父母。而廉长吏或鲜焉。天下之情。报与施而已。盖其本必出于道理。而其末归于利害。今以物予人曰。宁彼不报。吾不可以不施。此道理之说也。或欲其勿予而予之曰。予之冀其惠我也。不予惧其怨我也。此利害之说也。故喻于道理者。尚矣。凡为长吏而不廉者。直不喻利害焉耳。夫惠莫难于下。怨莫易于上。故父母之爱子也。而子之爱父母常不及。况民与长吏。固路人也。况上视下不如己。则下视上将路人之不若也。上取之厚而下愈欲其薄。上予之薄而下愈欲其厚。始则纷然而呶。中则骚然而讧。终乃奋然勃然而继之也。至是而不听则乱矣。听之则权在于民。而长吏从之。向之厚者。惟恐其不薄。而薄者惟恐其不厚。视其廪。萧然无一物。天下之至廉也。而民犹龂龂然不已。其利害何如也。若夫天灾流行。岁且荐饥。当此之时。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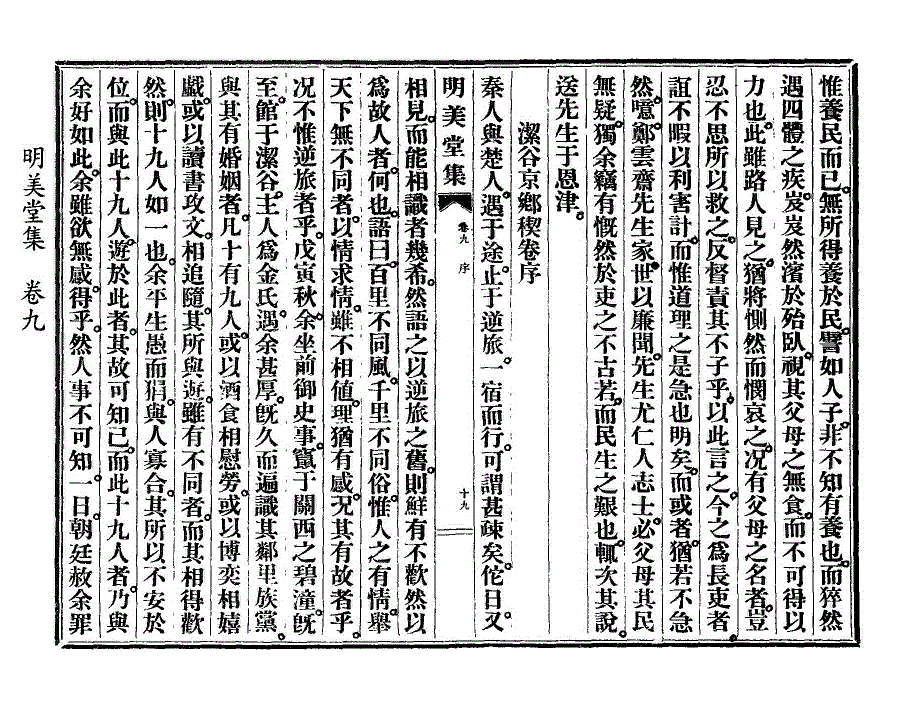 惟养民而已。无所得养于民。譬如人子。非不知有养也。而猝然遇四体之疾。岌岌然滨于殆卧。视其父母之无食。而不可得以力也。此虽路人见之。犹将恻然而悯哀之。况有父母之名者。岂忍不思所以救之。反督责其不子乎。以此言之。今之为长吏者。谊不暇以利害计。而惟道理之是急也明矣。而或者。犹若不急然。噫。郑云斋先生家。世以廉闻。先生尤仁人志士。必父母其民无疑。独余窃有慨然于吏之不古若。而民生之艰也。辄次其说。送先生于恩津。
惟养民而已。无所得养于民。譬如人子。非不知有养也。而猝然遇四体之疾。岌岌然滨于殆卧。视其父母之无食。而不可得以力也。此虽路人见之。犹将恻然而悯哀之。况有父母之名者。岂忍不思所以救之。反督责其不子乎。以此言之。今之为长吏者。谊不暇以利害计。而惟道理之是急也明矣。而或者。犹若不急然。噫。郑云斋先生家。世以廉闻。先生尤仁人志士。必父母其民无疑。独余窃有慨然于吏之不古若。而民生之艰也。辄次其说。送先生于恩津。洁谷京乡稧卷序
秦人与楚人。遇于途。止于逆旅。一宿而行。可谓甚疏矣。佗日。又相见。而能相识者几希。然语之以逆旅之旧。则鲜有不欢然以为故人者。何也。语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惟人之有情。举天下无不同者。以情求情。虽不相值。理犹有感。况其有故者乎。况不惟逆旅者乎。戊寅秋。余坐前御史事。窜于关西之碧潼。既至。馆于洁谷。主人为金氏。遇余甚厚。既久而遍识其邻里族党。与其有婚姻者。凡十有九人。或以酒食相慰劳。或以博奕相嬉戏。或以读书攻文。相追随。其所与游。虽有不同者。而其相得欢然。则十九人如一也。余平生愚而狷。与人寡合。其所以不安于位。而与此十九人。游于此者。其故可知已。而此十九人者。乃与余好如此。余虽欲无感。得乎。然人事不可知。一日。朝廷赦余罪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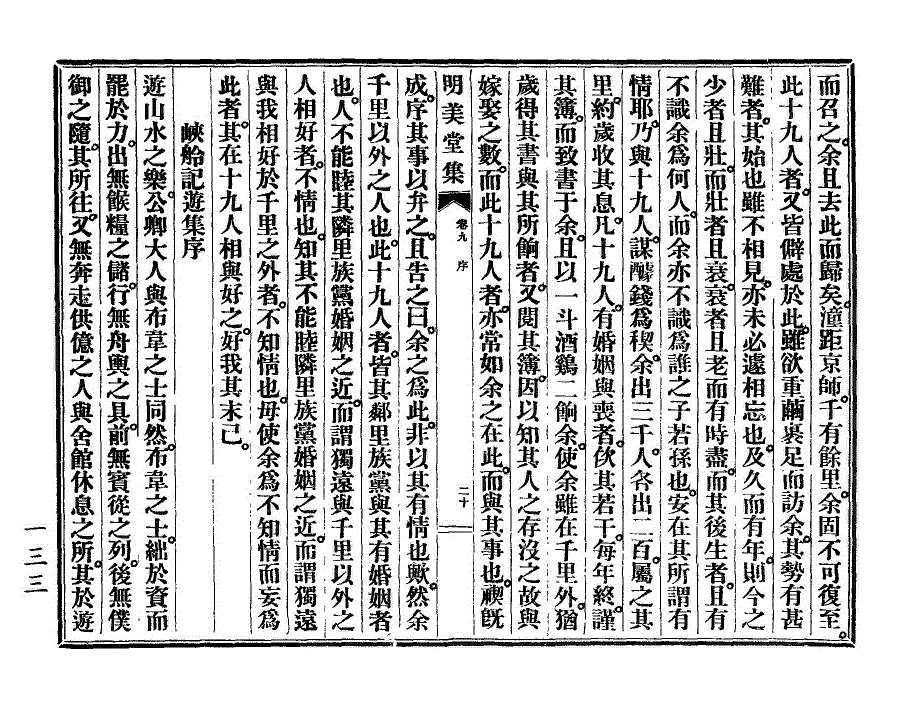 而召之。余且去此而归矣。潼距京师。千有馀里。余固不可复至。此十九人者。又皆僻处于此。虽欲重茧裹足而访余。其势有甚难者。其始也虽不相见。亦未必遽相忘也。及久而有年。则今之少者且壮。而壮者且衰。衰者且老而有时尽。而其后生者。且有不识余为何人。而余亦不识为谁之子若孙也。安在其所谓有情耶。乃与十九人。谋醵钱为稧。余出三千。人各出二百。属之其里。约岁收其息。凡十九人。有婚姻与丧者。佽其若干。每年终。谨其簿。而致书于余。且以一斗酒鸡二饷余。使余虽在千里外。犹岁得其书与其所饷者。又阅其簿。因以知其人之存没之故与嫁娶之数。而此十九人者。亦常如余之在此。而与其事也。禊既成。序其事以弁之。且告之曰。余之为此。非以其有情也欤。然余千里以外之人也。此十九人者。皆其邻里族党与其有婚姻者也。人不能睦其邻里族党婚姻之近。而谓独远与千里以外之人相好者。不情也。知其不能睦邻里族党婚姻之近。而谓独远与我相好于千里之外者。不知情也。毋使余为不知情而妄为此者。其在十九人相与好之。好我其末已。
而召之。余且去此而归矣。潼距京师。千有馀里。余固不可复至。此十九人者。又皆僻处于此。虽欲重茧裹足而访余。其势有甚难者。其始也虽不相见。亦未必遽相忘也。及久而有年。则今之少者且壮。而壮者且衰。衰者且老而有时尽。而其后生者。且有不识余为何人。而余亦不识为谁之子若孙也。安在其所谓有情耶。乃与十九人。谋醵钱为稧。余出三千。人各出二百。属之其里。约岁收其息。凡十九人。有婚姻与丧者。佽其若干。每年终。谨其簿。而致书于余。且以一斗酒鸡二饷余。使余虽在千里外。犹岁得其书与其所饷者。又阅其簿。因以知其人之存没之故与嫁娶之数。而此十九人者。亦常如余之在此。而与其事也。禊既成。序其事以弁之。且告之曰。余之为此。非以其有情也欤。然余千里以外之人也。此十九人者。皆其邻里族党与其有婚姻者也。人不能睦其邻里族党婚姻之近。而谓独远与千里以外之人相好者。不情也。知其不能睦邻里族党婚姻之近。而谓独远与我相好于千里之外者。不知情也。毋使余为不知情而妄为此者。其在十九人相与好之。好我其末已。峡舲记游集序
游山水之乐。公卿大人与布韦之士同然。布韦之士。绌于资而罢于力。出无糇粮之储。行无舟舆之具。前无宾从之列。后无仆御之随。其所往。又无奔走供亿之人与舍馆休息之所。其于游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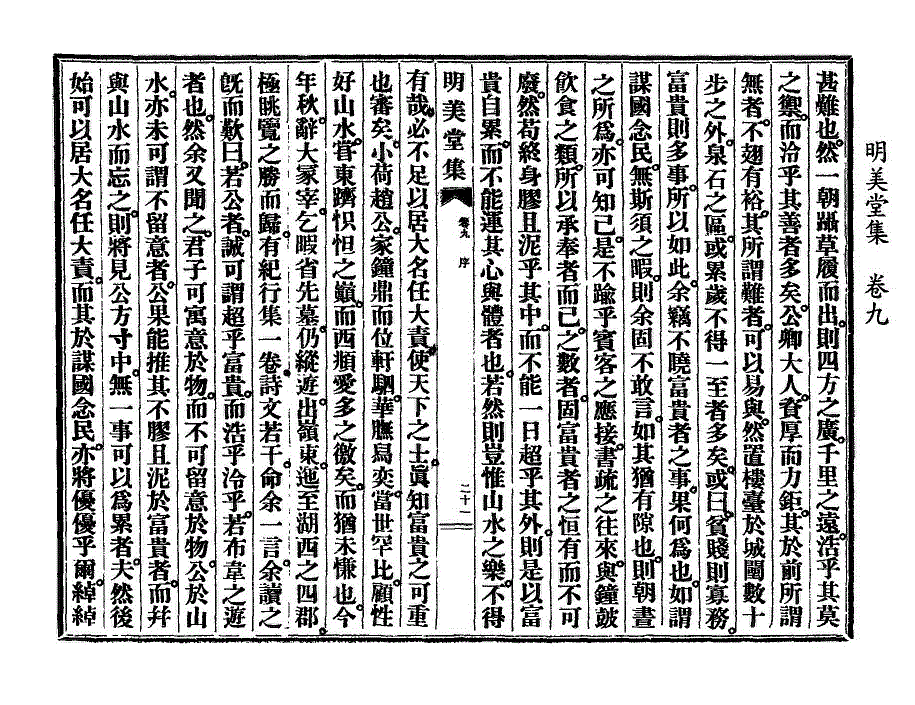 甚难也。然一朝蹑草履而出。则四方之广。千里之远。浩乎其莫之御。而泠乎其善者多矣。公卿大人。资厚而力钜。其于前所谓无者。不翅有裕。其所谓难者。可以易与。然置楼台于城闉数十步之外。泉石之区。或累岁不得一至者多矣。或曰。贫贱则寡务。富贵则多事。所以如此。余窃不晓富贵者之事。果何为也。如谓谋国念民。无斯须之暇。则余固不敢言。如其犹有隙也。则朝昼之所为。亦可知已。是不踰乎宾客之应接。书疏之往来。与钟鼓饮食之类。所以承奉者而已。之数者。固富贵者之恒有而不可废。然苟终身胶且泥乎其中。而不能一日超乎其外。则是以富贵自累。而不能运其心与体者也。若然则岂惟山水之乐。不得有哉。必不足以居大名任大责。使天下之士。真知富贵之可重也审矣。小荷赵公。家钟鼎而位轩驷。华膴舄奕。当世罕比。顾性好山水。尝东跻怾怛之巅。而西頫爱多之徼矣。而犹未慊也。今年秋。辞大冢宰。乞暇省先墓。仍纵游。出岭东。迤至湖西之四郡。极眺览之胜而归。有纪行集一卷。诗文若干。命余一言。余读之既而叹曰。若公者。诚可谓超乎富贵。而浩乎泠乎。若布韦之游者也。然余又闻之。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公于山水。亦未可谓不留意者。公果能推其不胶且泥于富贵者。而并与山水而忘之。则将见公方寸中。无一事可以为累者。夫然后始可以居大名任大责。而其于谋国念民。亦将优优乎尔。绰绰
甚难也。然一朝蹑草履而出。则四方之广。千里之远。浩乎其莫之御。而泠乎其善者多矣。公卿大人。资厚而力钜。其于前所谓无者。不翅有裕。其所谓难者。可以易与。然置楼台于城闉数十步之外。泉石之区。或累岁不得一至者多矣。或曰。贫贱则寡务。富贵则多事。所以如此。余窃不晓富贵者之事。果何为也。如谓谋国念民。无斯须之暇。则余固不敢言。如其犹有隙也。则朝昼之所为。亦可知已。是不踰乎宾客之应接。书疏之往来。与钟鼓饮食之类。所以承奉者而已。之数者。固富贵者之恒有而不可废。然苟终身胶且泥乎其中。而不能一日超乎其外。则是以富贵自累。而不能运其心与体者也。若然则岂惟山水之乐。不得有哉。必不足以居大名任大责。使天下之士。真知富贵之可重也审矣。小荷赵公。家钟鼎而位轩驷。华膴舄奕。当世罕比。顾性好山水。尝东跻怾怛之巅。而西頫爱多之徼矣。而犹未慊也。今年秋。辞大冢宰。乞暇省先墓。仍纵游。出岭东。迤至湖西之四郡。极眺览之胜而归。有纪行集一卷。诗文若干。命余一言。余读之既而叹曰。若公者。诚可谓超乎富贵。而浩乎泠乎。若布韦之游者也。然余又闻之。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公于山水。亦未可谓不留意者。公果能推其不胶且泥于富贵者。而并与山水而忘之。则将见公方寸中。无一事可以为累者。夫然后始可以居大名任大责。而其于谋国念民。亦将优优乎尔。绰绰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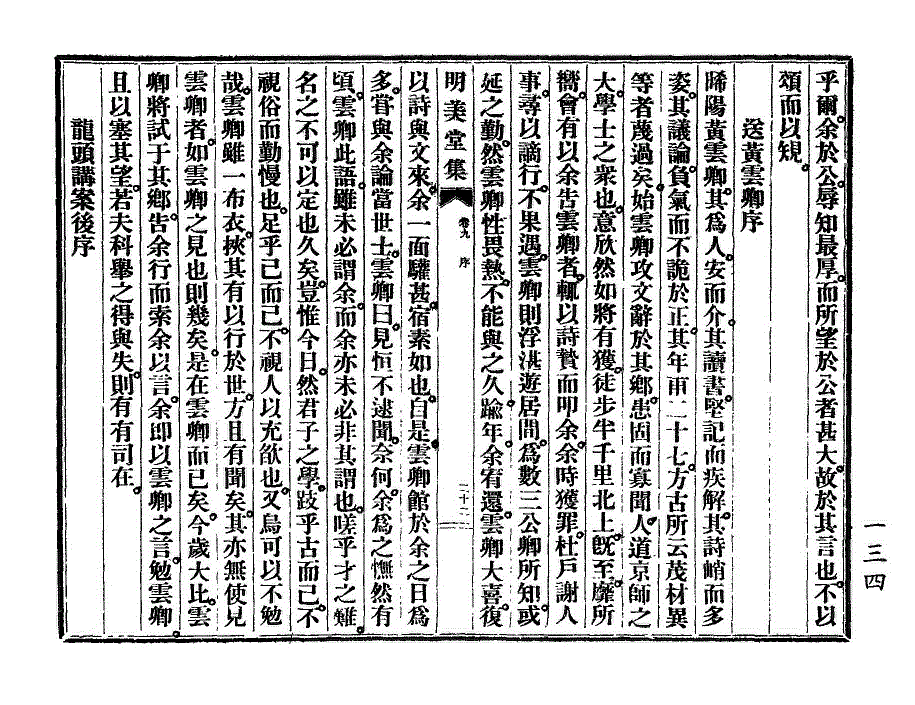 乎尔。余于公。辱知最厚。而所望于公者甚大。故于其言也。不以颂而以规。
乎尔。余于公。辱知最厚。而所望于公者甚大。故于其言也。不以颂而以规。送黄云卿序
晞阳黄云卿。其为人。安而介。其读书。坚记而疾解。其诗峭而多姿。其议论。负气而不诡于正。其年甫二十七。方古所云茂材异等者蔑过矣。始云卿攻文辞于其乡。患固而寡闻。人道京师之大。学士之众也。意欣然如将有获。徒步半千里北上。既至。靡所向。会有以余告云卿者。辄以诗贽而叩余。余时获罪。杜户谢人事。寻以谪行。不果遇。云卿则浮湛游居间。为数三公卿所知。或延之勤。然云卿性畏热。不能与之久。踰年。余宥还。云卿大喜。复以诗与文来。余一面驩甚。宿素如也。自是。云卿馆于余之日为多。尝与余论当世士。云卿曰。见恒不逮闻。奈何。余为之怃然有顷。云卿此语。虽未必谓余。而余亦未必非其谓也。嗟乎才之难。名之不可以定也久矣。岂惟今日。然君子之学。跂乎古而已。不视俗而勤慢也。足乎己而已。不视人以充欿也。又乌可以不勉哉。云卿虽一布衣。挟其有以行于世。方且有闻矣。其亦无使见云卿者。如云卿之见也则几矣。是在云卿而已矣。今岁大比。云卿将试于其乡。告余行而索余以言。余即以云卿之言。勉云卿。且以塞其望。若夫科举之得与失。则有有司在。
龙头讲案后序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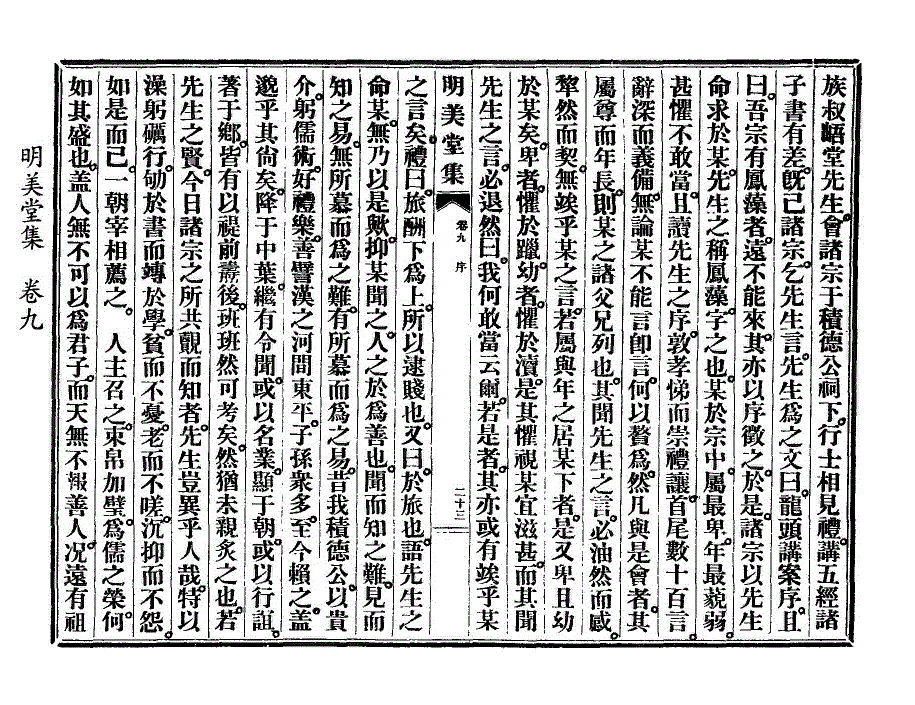 族叔峿堂先生。会诸宗于积德公祠下。行士相见礼。讲五经诸子书有差。既已诸宗。乞先生言。先生为之文曰。龙头讲案序。且曰。吾宗有凤藻者。远不能来。其亦以序徵之。于是。诸宗以先生命求于某。先生之称凤藻。字之也。某于宗中。属最卑。年最藐弱。甚惧不敢当。且读先生之序。敦孝悌而崇礼让。首尾数十百言。辞深而义备。无论某不能言即言。何以赘为。然凡与是会者。其属尊而年长。则某之诸父兄列也。其闻先生之言。必油然而感。犁然而契。无俟乎某之言。若属与年之居某下者。是又卑且幼于某矣。卑者。惧于躐。幼者。惧于渎。是其惧视某宜滋甚。而其闻先生之言。必退然曰。我何敢当云尔。若是者。其亦或有俟乎某之言矣。礼曰。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又曰。于旅也。语先生之命某。无乃以是欤。抑某闻之。人之于为善也。闻而知之难。见而知之易。无所慕而为之难。有所慕而为之易。昔我积德公。以贵介。躬儒术。好礼乐。善譬汉之河间东平。子孙众多。至今赖之。盖邈乎其尚矣。降于中叶。继有令闻。或以名业。显于朝。或以行谊。著于乡。皆有以禔前焘后。班班然可考矣。然犹未亲炙之也。若先生之贤。今日诸宗之所共觌而知者。先生岂异乎人哉。特以澡躬砺行。劬于书而竱于学。贫而不忧。老而不嗟。沉抑而不怨。如是而已。一朝宰相荐之。 人主召之。束帛加璧。为儒之荣。何如其盛也。盖人无不可以为君子。而天无不报善人。况远有祖
族叔峿堂先生。会诸宗于积德公祠下。行士相见礼。讲五经诸子书有差。既已诸宗。乞先生言。先生为之文曰。龙头讲案序。且曰。吾宗有凤藻者。远不能来。其亦以序徵之。于是。诸宗以先生命求于某。先生之称凤藻。字之也。某于宗中。属最卑。年最藐弱。甚惧不敢当。且读先生之序。敦孝悌而崇礼让。首尾数十百言。辞深而义备。无论某不能言即言。何以赘为。然凡与是会者。其属尊而年长。则某之诸父兄列也。其闻先生之言。必油然而感。犁然而契。无俟乎某之言。若属与年之居某下者。是又卑且幼于某矣。卑者。惧于躐。幼者。惧于渎。是其惧视某宜滋甚。而其闻先生之言。必退然曰。我何敢当云尔。若是者。其亦或有俟乎某之言矣。礼曰。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又曰。于旅也。语先生之命某。无乃以是欤。抑某闻之。人之于为善也。闻而知之难。见而知之易。无所慕而为之难。有所慕而为之易。昔我积德公。以贵介。躬儒术。好礼乐。善譬汉之河间东平。子孙众多。至今赖之。盖邈乎其尚矣。降于中叶。继有令闻。或以名业。显于朝。或以行谊。著于乡。皆有以禔前焘后。班班然可考矣。然犹未亲炙之也。若先生之贤。今日诸宗之所共觌而知者。先生岂异乎人哉。特以澡躬砺行。劬于书而竱于学。贫而不忧。老而不嗟。沉抑而不怨。如是而已。一朝宰相荐之。 人主召之。束帛加璧。为儒之荣。何如其盛也。盖人无不可以为君子。而天无不报善人。况远有祖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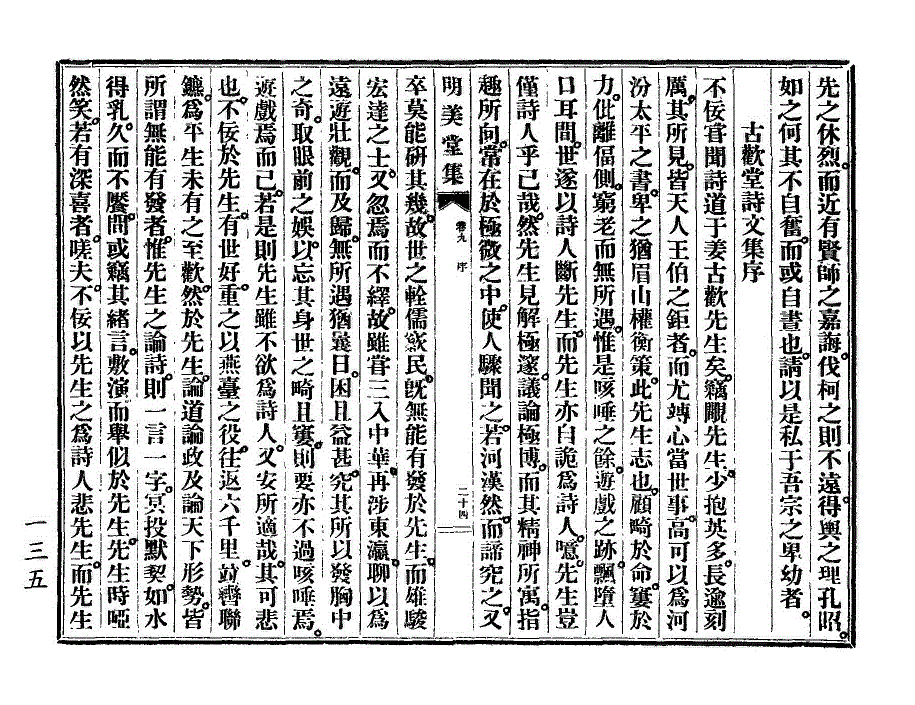 先之休烈。而近有贤师之嘉诲。伐柯之则不远。得舆之理孔昭。如之何其不自奋。而或自昼(一作画)也。请以是私于吾宗之卑幼者。
先之休烈。而近有贤师之嘉诲。伐柯之则不远。得舆之理孔昭。如之何其不自奋。而或自昼(一作画)也。请以是私于吾宗之卑幼者。古欢堂诗文集序
不佞尝闻诗道于姜古欢先生矣。窃覸先生。少抱英多。长逾刻厉。其所见。皆天人王伯之钜者。而尤竱心当世事。高可以为河汾太平之书。卑之犹眉山权衡策。此先生志也。顾畸于命。窭于力。仳离偪侧。穷老而无所遇。惟是咳唾之馀。游戏之迹。飘堕人口耳间。世遂以诗人断先生。而先生亦自诡为诗人。噫。先生岂仅诗人乎已哉。然先生见解极邃。议论极博。而其精神所寓。指趣所向。常在于极微之中。使人骤闻之。若河汉然。而谛究之。又卒莫能研其几。故世之辁儒窾民。既无能有发于先生。而雄骏宏达之士。又忽焉而不绎。故虽尝三入中华。再涉东瀛。聊以为远游壮观。而及归。无所遇犹曩日。困且益甚。究其所以发胸中之奇。取眼前之娱。以忘其身世之畸且窭。则要亦不过咳唾焉。游戏焉而已。若是则先生虽不欲为诗人。又安所适哉。其可悲也。不佞于先生。有世好。重之以燕台之役。往返六千里。并辔联镳。为平生未有之至欢。然于先生。论道论政及论天下形势。皆所谓无能有发者。惟先生之论诗。则一言一字。冥投默契。如水得乳。久而不餍。间或窃其绪言。敷演而举似于先生。先生时哑然笑。若有深喜者。嗟夫。不佞以先生之为诗人悲先生。而先生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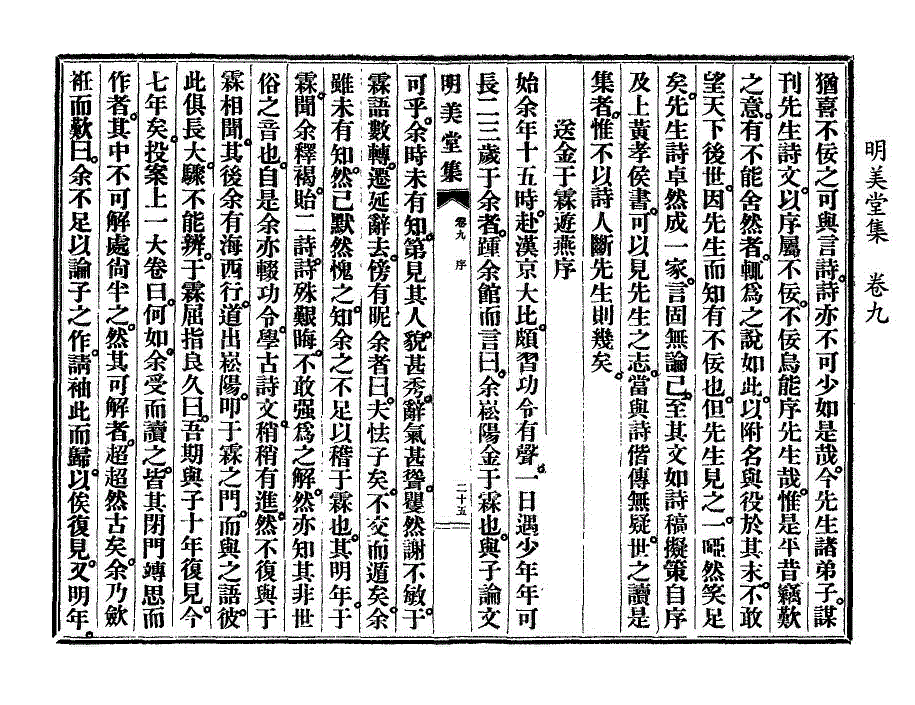 犹喜不佞之可与言诗。诗亦不可少如是哉。今先生诸弟子。谋刊先生诗文。以序属不佞。不佞乌能序先生哉。惟是平昔窃叹之意。有不能舍然者。辄为之说如此。以附名与役于其末。不敢望天下后世。因先生而知有不佞也。但先生见之。一哑然笑足矣。先生诗卓然成一家。言固无论已。至其文如诗稿拟策自序及上黄孝侯书。可以见先生之志。当与诗偕传无疑。世之读是集者。惟不以诗人断先生则几矣。
犹喜不佞之可与言诗。诗亦不可少如是哉。今先生诸弟子。谋刊先生诗文。以序属不佞。不佞乌能序先生哉。惟是平昔窃叹之意。有不能舍然者。辄为之说如此。以附名与役于其末。不敢望天下后世。因先生而知有不佞也。但先生见之。一哑然笑足矣。先生诗卓然成一家。言固无论已。至其文如诗稿拟策自序及上黄孝侯书。可以见先生之志。当与诗偕传无疑。世之读是集者。惟不以诗人断先生则几矣。送金于霖游燕序
始余年十五时。赴汉京大比。颇习功令有声。一日遇少年年可长二三岁于余者。踵余馆而言曰。余崧阳金于霖也。与子论文可乎。余时未有知。第见其人。貌甚秀。辞气甚耸。矍然谢不敏。于霖语数转。迁延辞去。傍有昵余者曰。夫怯子矣。不交而遁矣。余虽未有知。然已默然愧之。知余之不足以稽于霖也。其明年。于霖。闻余释褐。贻二诗。诗殊艰晦。不敢强为之解。然亦知其非世俗之音也。自是余亦辍功令。学古诗文。稍稍有进。然不复与于霖相闻。其后余有海西行。道出崧阳。叩于霖之门。而与之语。彼此俱长大。骤不能辨。于霖屈指良久曰。吾期与子十年复见。今七年矣。投案上一大卷曰。何如。余受而读之。皆其闭门竱思而作者。其中不可解处尚半之。然其可解者。超超然古矣。余乃敛衽而叹曰。余不足以论子之作。请袖此而归。以俟复见。又明年。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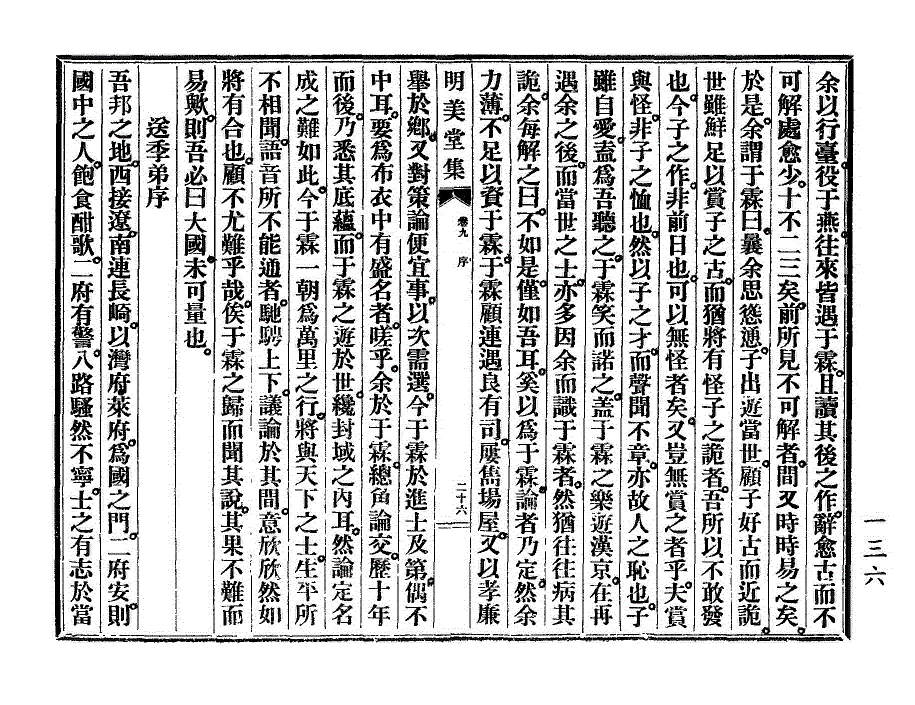 余以行台。役于燕。往来皆遇于霖。且读其后之作。辞愈古而不可解处愈少。十不二三矣。前所见不可解者。间又时时易之矣。于是。余谓于霖曰。曩余思怂恿。子出游当世。顾子好古而近诡。世虽鲜足以赏子之古。而犹将有怪子之诡者。吾所以不敢发也。今子之作。非前日也。可以无怪者矣。又岂无赏之者乎。夫赏与怪。非子之恤也。然以子之才。而声闻不章。亦故人之耻也。子虽自爱。盍为吾听之。于霖笑而诺之。盖于霖之乐游汉京。在再遇余之后。而当世之士。亦多因余而识于霖者。然犹往往病其诡。余每解之曰。不如是。仅如吾耳。奚以为于霖。论者乃定。然余力薄。不足以资于霖。于霖顾连遇良有司。屡隽场屋。又以孝廉举于乡。又对策论便宜事。以次需选。今于霖于进士及第。偶不中耳。要为布衣中有盛名者。嗟乎。余于于霖。总角论交。历十年而后。乃悉其底蕴。而于霖之游于世。才封域之内耳。然论定名成之难如此。今于霖一朝为万里之行。将与天下之士。生平所不相闻。语音所不能通者。驰骋上下。议论于其间。意欣欣然如将有合也。顾不尤难乎哉。俟于霖之归而闻其说。其果不难而易欤。则吾必曰大国。未可量也。
余以行台。役于燕。往来皆遇于霖。且读其后之作。辞愈古而不可解处愈少。十不二三矣。前所见不可解者。间又时时易之矣。于是。余谓于霖曰。曩余思怂恿。子出游当世。顾子好古而近诡。世虽鲜足以赏子之古。而犹将有怪子之诡者。吾所以不敢发也。今子之作。非前日也。可以无怪者矣。又岂无赏之者乎。夫赏与怪。非子之恤也。然以子之才。而声闻不章。亦故人之耻也。子虽自爱。盍为吾听之。于霖笑而诺之。盖于霖之乐游汉京。在再遇余之后。而当世之士。亦多因余而识于霖者。然犹往往病其诡。余每解之曰。不如是。仅如吾耳。奚以为于霖。论者乃定。然余力薄。不足以资于霖。于霖顾连遇良有司。屡隽场屋。又以孝廉举于乡。又对策论便宜事。以次需选。今于霖于进士及第。偶不中耳。要为布衣中有盛名者。嗟乎。余于于霖。总角论交。历十年而后。乃悉其底蕴。而于霖之游于世。才封域之内耳。然论定名成之难如此。今于霖一朝为万里之行。将与天下之士。生平所不相闻。语音所不能通者。驰骋上下。议论于其间。意欣欣然如将有合也。顾不尤难乎哉。俟于霖之归而闻其说。其果不难而易欤。则吾必曰大国。未可量也。送季弟序
吾邦之地。西接辽。南连长崎。以湾府,莱府。为国之门。二府安。则国中之人。饱食酣歌。二府有警。八路骚然不宁。士之有志于当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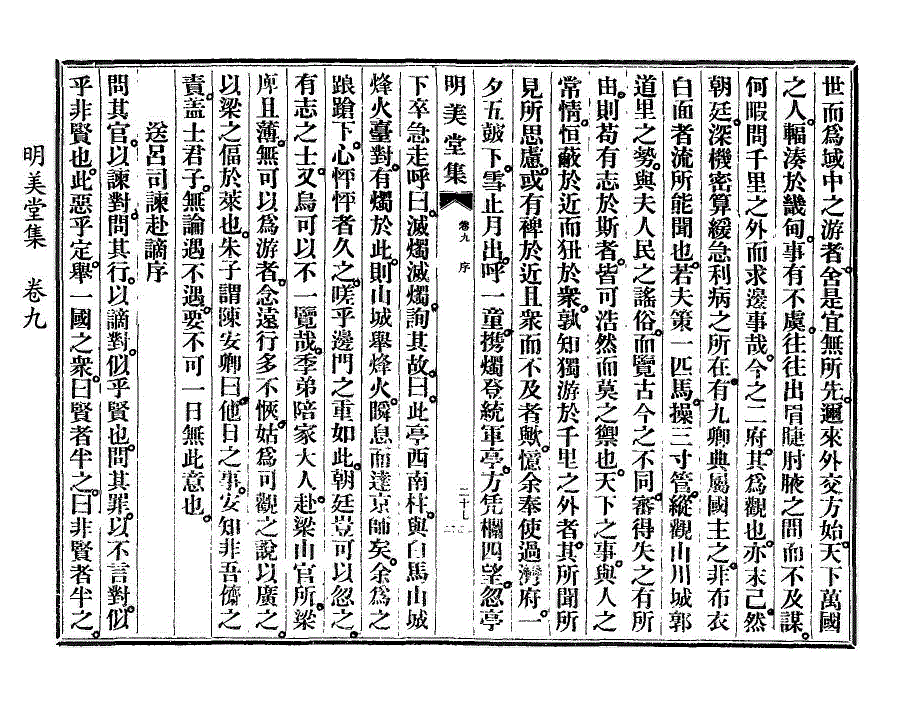 世而为域中之游者。舍是宜无所先。迩来外交方始。天下万国之人。辐凑于畿甸。事有不虞。往往出眉睫肘腋之间而不及谋。何暇问千里之外而求边事哉。今之二府。其为观也。亦末已。然朝廷。深机密算缓急利病之所在。有九卿典属国主之。非布衣白面者流所能闻也。若夫策一匹马。操三寸管。纵观山川城郭道里之势。与夫人民之谣俗。而览古今之不同。审得失之有所由。则苟有志于斯者。皆可浩然而莫之御也。天下之事。与人之常情。恒蔽于近而狃于众。孰知独游于千里之外者。其所闻所见所思虑。或有裨于近且众而不及者欤。忆余奉使过湾府。一夕五鼓下。雪止月出。呼一童。携烛登统军亭。方凭栏四望。忽亭下卒急走呼曰。灭烛灭烛。询其故。曰。此亭西南柱。与白马山城烽火台对。有烛于此。则山城举烽火。瞬息而达京师矣。余为之踉跄下。心怦怦者久之。嗟乎边门之重如此。朝廷岂可以忽之。有志之士。又乌可以不一览哉。季弟陪家大人。赴梁山官所。梁庳且薄。无可以为游者。念远行多不惬。姑为可观之说以广之。以梁之偪于莱也。朱子谓陈安卿曰。他日之事。安知非吾侪之责。盖士君子。无论遇不遇。要不可一日无此意也。
世而为域中之游者。舍是宜无所先。迩来外交方始。天下万国之人。辐凑于畿甸。事有不虞。往往出眉睫肘腋之间而不及谋。何暇问千里之外而求边事哉。今之二府。其为观也。亦末已。然朝廷。深机密算缓急利病之所在。有九卿典属国主之。非布衣白面者流所能闻也。若夫策一匹马。操三寸管。纵观山川城郭道里之势。与夫人民之谣俗。而览古今之不同。审得失之有所由。则苟有志于斯者。皆可浩然而莫之御也。天下之事。与人之常情。恒蔽于近而狃于众。孰知独游于千里之外者。其所闻所见所思虑。或有裨于近且众而不及者欤。忆余奉使过湾府。一夕五鼓下。雪止月出。呼一童。携烛登统军亭。方凭栏四望。忽亭下卒急走呼曰。灭烛灭烛。询其故。曰。此亭西南柱。与白马山城烽火台对。有烛于此。则山城举烽火。瞬息而达京师矣。余为之踉跄下。心怦怦者久之。嗟乎边门之重如此。朝廷岂可以忽之。有志之士。又乌可以不一览哉。季弟陪家大人。赴梁山官所。梁庳且薄。无可以为游者。念远行多不惬。姑为可观之说以广之。以梁之偪于莱也。朱子谓陈安卿曰。他日之事。安知非吾侪之责。盖士君子。无论遇不遇。要不可一日无此意也。送吕司谏赴谪序
问其官。以谏对。问其行。以谪对。似乎贤也。问其罪。以不言对。似乎非贤也。此恶乎定。举一国之众。曰贤者半之。曰非贤者半之。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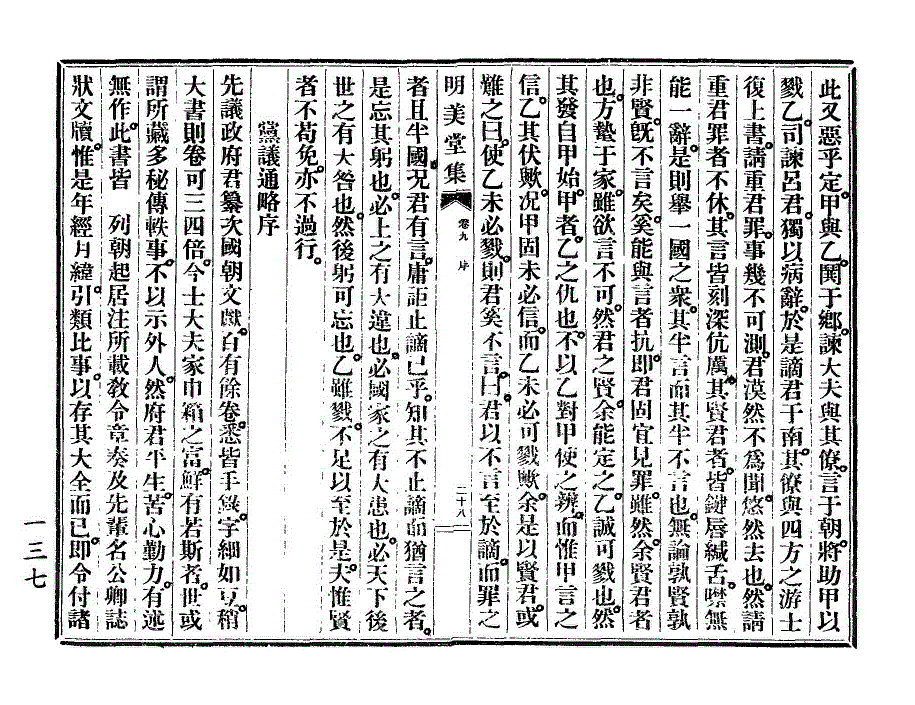 此又恶乎定。甲与乙。鬨于乡。谏大夫与其僚。言于朝。将助甲以戮乙。司谏吕君。独以病辞。于是谪君于南。其僚与四方之游士复上书。请重君罪。事几不可测。君漠然不为闻。悠然去也。然请重君罪者不休。其言皆刻深伉厉。其贤君者。皆键唇缄舌。噤无能一辞。是则举一国之众。其半言而其半不言也。无论孰贤孰非贤。既不言矣。奚能与言者抗。即君固宜见罪。虽然。余贤君者也。方蛰于家。虽欲言不可。然君之贤。余能定之。乙诚可戮也。然其发自甲始。甲者。乙之仇也。不以乙对甲使之辨。而惟甲言之信。乙其伏欤。况甲固未必信。而乙未必可戮欤。余是以贤君。或难之曰。使乙未必戮。则君奚不言。曰。君以不言至于谪。而罪之者且半国。况君有言。庸讵止谪已乎。知其不止谪而犹言之者。是忘其躬也。必上之有大违也。必国家之有大患也。必天下后世之有大咎也。然后躬可忘也。乙虽戮。不足以至于是。夫惟贤者不苟免。亦不过行。
此又恶乎定。甲与乙。鬨于乡。谏大夫与其僚。言于朝。将助甲以戮乙。司谏吕君。独以病辞。于是谪君于南。其僚与四方之游士复上书。请重君罪。事几不可测。君漠然不为闻。悠然去也。然请重君罪者不休。其言皆刻深伉厉。其贤君者。皆键唇缄舌。噤无能一辞。是则举一国之众。其半言而其半不言也。无论孰贤孰非贤。既不言矣。奚能与言者抗。即君固宜见罪。虽然。余贤君者也。方蛰于家。虽欲言不可。然君之贤。余能定之。乙诚可戮也。然其发自甲始。甲者。乙之仇也。不以乙对甲使之辨。而惟甲言之信。乙其伏欤。况甲固未必信。而乙未必可戮欤。余是以贤君。或难之曰。使乙未必戮。则君奚不言。曰。君以不言至于谪。而罪之者且半国。况君有言。庸讵止谪已乎。知其不止谪而犹言之者。是忘其躬也。必上之有大违也。必国家之有大患也。必天下后世之有大咎也。然后躬可忘也。乙虽戮。不足以至于是。夫惟贤者不苟免。亦不过行。党议通略序
先议政府君纂次国朝文献。百有馀卷。悉皆手录。字细如豆。稍大书则卷可三四倍。今士大夫家巾箱之富。鲜有若斯者。世或谓所藏多秘传轶事。不以示外人。然府君平生。苦心勤力。有述无作。此书皆 列朝起居注所载教令章奏及先辈名公卿志状文牍。惟是年经月纬。引类比事。以存其大全而已。即令付诸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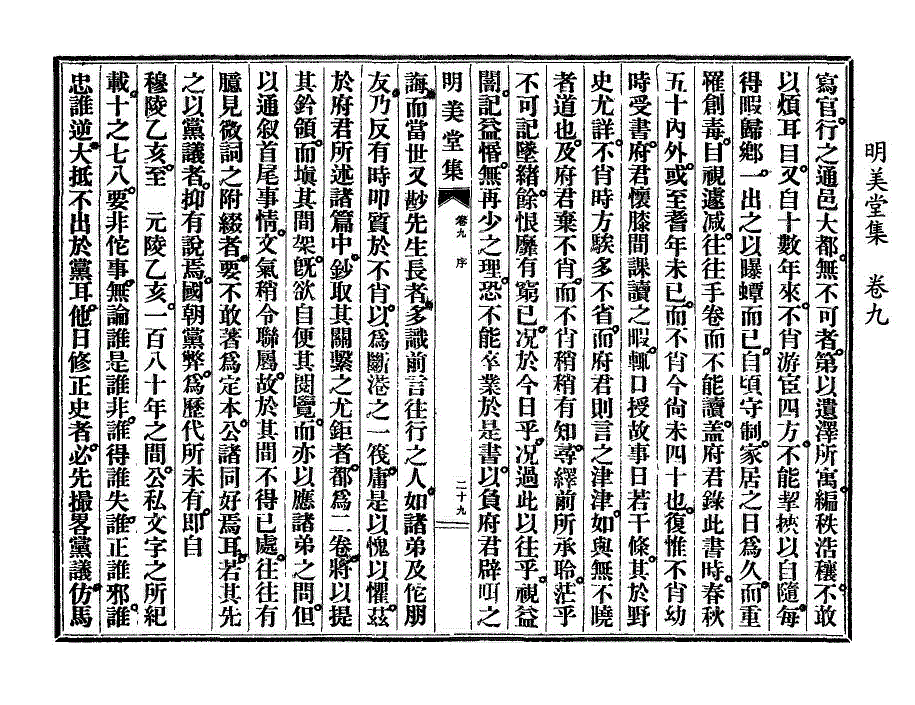 写官。行之通邑大都。无不可者。第以遗泽所寓。编秩浩穰。不敢以烦耳目。又自十数年来。不肖游宦四方。不能挈挟以自随。每得暇归乡。一出之以曝蟫而已。自顷守制。家居之日为久。而重罹创毒。目视遽减。往往手卷而不能读。盖府君录此书时。春秋五十内外。或至耆年未已。而不肖今尚未四十也。复惟不肖幼时受书。府君怀膝间课读之暇。辄口授故事日若干条。其于野史尤详。不肖时方騃多不省。而府君则言之津津。如与无不晓者道也。及府君弃不肖。而不肖稍稍有知。寻绎前所承聆。茫乎不可记坠绪。馀恨靡有穷已。况于今日乎。况过此以往乎。视益闇。记益悯。无再少之理。恐不能卒业于是书。以负府君辟咡之诲。而当世又鲜先生长者。多识前言往行之人。如诸弟及佗朋友。乃反有时叩质于不肖。以为断港之一筏。庸是以愧以惧。兹于府君所述诸篇中。钞取其关系之尤钜者。都为二卷。将以提其钤领。而填其间架。既欲自便其阅览。而亦以应诸弟之问。但以通叙首尾事情。文气稍令联属。故于其间不得已处。往往有臆见微词之附缀者。要不敢著为定本。公诸同好焉耳。若其先之以党议者。抑有说焉。国朝党弊。为历代所未有。即自 穆陵乙亥。至 元陵乙亥。一百八十年之间。公私文字之所纪载。十之七八。要非佗事。无论谁是谁非。谁得谁失。谁正谁邪。谁忠谁逆。大抵不出于党耳。他日修正史者。必先撮略党议。仿马
写官。行之通邑大都。无不可者。第以遗泽所寓。编秩浩穰。不敢以烦耳目。又自十数年来。不肖游宦四方。不能挈挟以自随。每得暇归乡。一出之以曝蟫而已。自顷守制。家居之日为久。而重罹创毒。目视遽减。往往手卷而不能读。盖府君录此书时。春秋五十内外。或至耆年未已。而不肖今尚未四十也。复惟不肖幼时受书。府君怀膝间课读之暇。辄口授故事日若干条。其于野史尤详。不肖时方騃多不省。而府君则言之津津。如与无不晓者道也。及府君弃不肖。而不肖稍稍有知。寻绎前所承聆。茫乎不可记坠绪。馀恨靡有穷已。况于今日乎。况过此以往乎。视益闇。记益悯。无再少之理。恐不能卒业于是书。以负府君辟咡之诲。而当世又鲜先生长者。多识前言往行之人。如诸弟及佗朋友。乃反有时叩质于不肖。以为断港之一筏。庸是以愧以惧。兹于府君所述诸篇中。钞取其关系之尤钜者。都为二卷。将以提其钤领。而填其间架。既欲自便其阅览。而亦以应诸弟之问。但以通叙首尾事情。文气稍令联属。故于其间不得已处。往往有臆见微词之附缀者。要不敢著为定本。公诸同好焉耳。若其先之以党议者。抑有说焉。国朝党弊。为历代所未有。即自 穆陵乙亥。至 元陵乙亥。一百八十年之间。公私文字之所纪载。十之七八。要非佗事。无论谁是谁非。谁得谁失。谁正谁邪。谁忠谁逆。大抵不出于党耳。他日修正史者。必先撮略党议。仿马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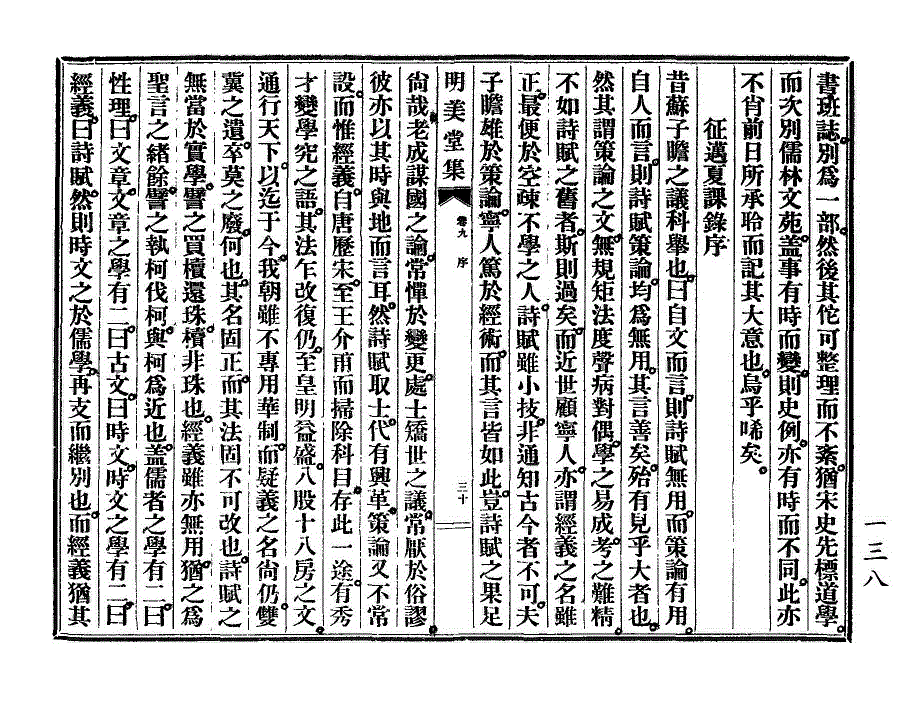 书,班志。别为一部。然后其佗可整理而不紊。犹宋史先标道学。而次别儒林文苑。盖事有时而变。则史例。亦有时而不同。此亦不肖前日所承聆而记其大意也。乌乎唏矣。
书,班志。别为一部。然后其佗可整理而不紊。犹宋史先标道学。而次别儒林文苑。盖事有时而变。则史例。亦有时而不同。此亦不肖前日所承聆而记其大意也。乌乎唏矣。征迈夏课录序
昔苏子瞻之议科举也。曰自文而言。则诗赋无用。而策论有用。自人而言。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其言善矣。殆有见乎大者也。然其谓策论之文。无规矩法度声病对偶。学之易成。考之难精。不如诗赋之旧者。斯则过矣。而近世顾宁人。亦谓经义之名虽正。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诗赋虽小技。非通知古今者不可。夫子瞻雄于策论。宁人笃于经术。而其言皆如此。岂诗赋之果足尚哉。老成谋国之论。常惮于变更。处士矫世之议。常厌于俗谬。彼亦以其时与地而言耳。然诗赋取士。代有兴革。策论又不常设。而惟经义。自唐历宋。至王介甫而扫除科目。存此一途。有秀才变学究之语。其法乍改复仍。至皇明益盛。八股十八房之文。通行天下。以迄于今。我朝虽不专用华制。而疑义之名尚仍。双冀之遗。卒莫之废。何也。其名固正。而其法固不可改也。诗赋之无当于实学。譬之买椟还珠。椟非珠也。经义虽亦无用。犹之为圣言之绪馀。譬之执柯伐柯。与柯为近也。盖儒者之学有二。曰性理。曰文章。文章之学有二。曰古文。曰时文。时文之学有二。曰经义。曰诗赋。然则时文之于儒学。再支而继别也。而经义犹其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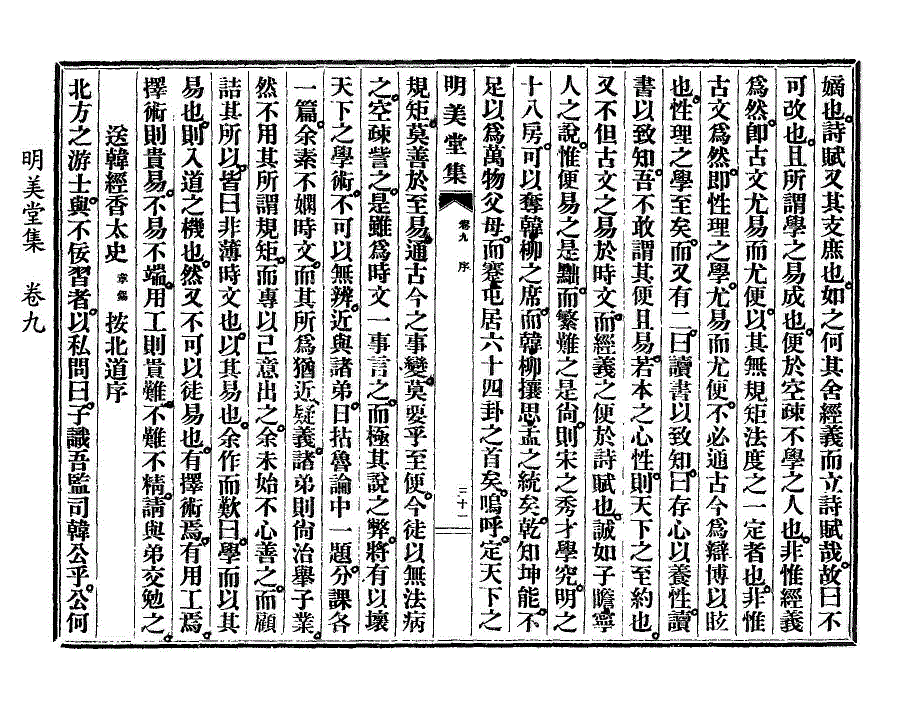 嫡也。诗赋又其支庶也。如之何其舍经义而立诗赋哉。故曰不可改也。且所谓学之易成也。便于空疏不学之人也。非惟经义为然。即古文尤易而尤便。以其无规矩法度之一定者也。非惟古文为然。即性理之学。尤易而尤便。不必通古今为辩博以眩也。性理之学至矣。而又有二。曰读书以致知。曰存心以养性。读书以致知。吾不敢谓其便且易。若本之心性。则天下之至约也。又不但古文之易于时文。而经义之便于诗赋也。诚如子瞻,宁人之说。惟便易之是黜。而繁难之是尚。则宋之秀才学究。明之十八房。可以夺韩,柳之席。而韩,柳攘思,孟之统矣。乾知坤能。不足以为万物父母。而蹇,屯居六十四卦之首矣。呜呼。定天下之规矩。莫善于至易。通古今之事变。莫要乎至便。今徒以无法病之。空疏訾之。是虽为时文一事言之。而极其说之弊。将有以坏天下之学术。不可以无辨。近与诸弟。日拈鲁论中一题。分课各一篇。余素不娴时文。而其所为犹近疑义。诸弟则尚治举子业。然不用其所谓规矩。而专以己意出之。余未始不心善之。而顾诘其所以。皆曰非薄时文也。以其易也。余作而叹曰。学而以其易也。则入道之机也。然又不可以徒易也。有择术焉。有用工焉。择术则贵易。不易不端。用工则贵难。不难不精。请与弟交勉之。
嫡也。诗赋又其支庶也。如之何其舍经义而立诗赋哉。故曰不可改也。且所谓学之易成也。便于空疏不学之人也。非惟经义为然。即古文尤易而尤便。以其无规矩法度之一定者也。非惟古文为然。即性理之学。尤易而尤便。不必通古今为辩博以眩也。性理之学至矣。而又有二。曰读书以致知。曰存心以养性。读书以致知。吾不敢谓其便且易。若本之心性。则天下之至约也。又不但古文之易于时文。而经义之便于诗赋也。诚如子瞻,宁人之说。惟便易之是黜。而繁难之是尚。则宋之秀才学究。明之十八房。可以夺韩,柳之席。而韩,柳攘思,孟之统矣。乾知坤能。不足以为万物父母。而蹇,屯居六十四卦之首矣。呜呼。定天下之规矩。莫善于至易。通古今之事变。莫要乎至便。今徒以无法病之。空疏訾之。是虽为时文一事言之。而极其说之弊。将有以坏天下之学术。不可以无辨。近与诸弟。日拈鲁论中一题。分课各一篇。余素不娴时文。而其所为犹近疑义。诸弟则尚治举子业。然不用其所谓规矩。而专以己意出之。余未始不心善之。而顾诘其所以。皆曰非薄时文也。以其易也。余作而叹曰。学而以其易也。则入道之机也。然又不可以徒易也。有择术焉。有用工焉。择术则贵易。不易不端。用工则贵难。不难不精。请与弟交勉之。送韩经香太史(章锡)按北道序
北方之游士。与不佞习者。以私问曰。子识吾监司韩公乎。公何
明美堂集卷九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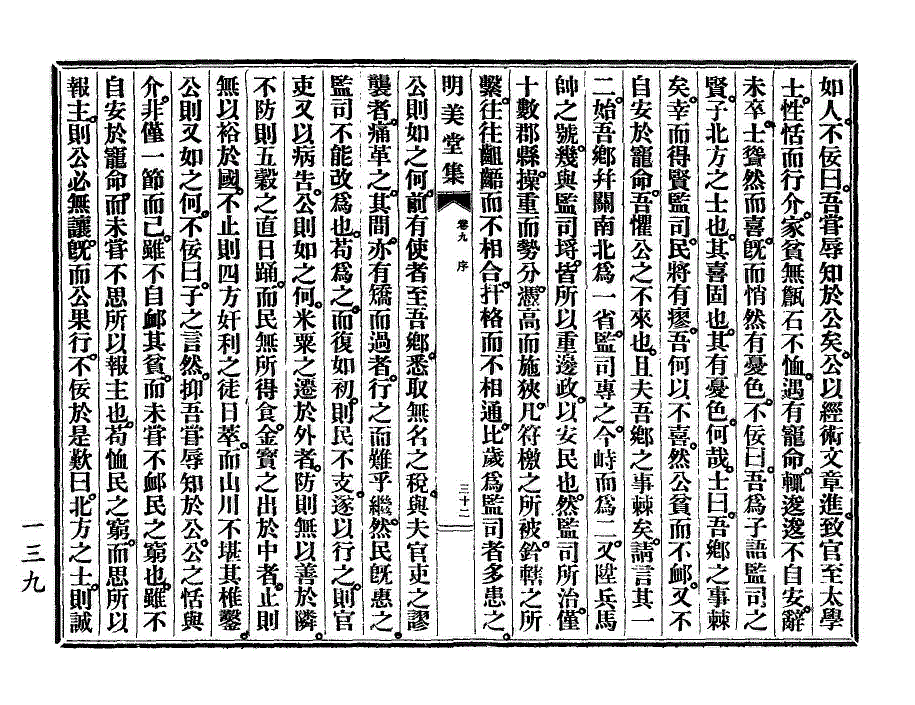 如人。不佞曰。吾尝辱知于公矣。公以经术文章进。致官至太学士。性恬而行介。家贫无甔石不恤。遇有宠命。辄逡逡不自安。辞未卒。士耸然而喜。既而悄然有忧色。不佞曰。吾为子语监司之贤。子北方之士也。其喜固也。其有忧色。何哉。士曰。吾乡之事棘矣。幸而得贤监司。民将有瘳。吾何以不喜。然公贫而不恤。又不自安于宠命。吾惧公之不来也。且夫吾乡之事棘矣。请言其一二。始吾乡并关南北为一省。监司专之。今峙而为二。又升兵马帅之号。几与监司埒。皆所以重边政。以安民也。然监司所治。仅十数郡县。操重而势分。凭高而施狭。凡符檄之所被。钤辖之所系。往往龃龉而不相合。捍格而不相通。比岁为监司者多患之。公则如之何。前有使者至吾乡。悉取无名之税。与夫官吏之谬袭者。痛革之。其间。亦有矫而过者。行之而难乎继。然民既惠之。监司不能改为也。苟为之。而复如初。则民不支。遂以行之。则官吏又以病告。公则如之何。米粟之迁于外者。防则无以善于邻。不防则五谷之直日踊。而民无所得食。金宝之出于中者。止则无以裕于国。不止则四方奸利之徒日萃。而山川不堪其椎凿。公则又如之何。不佞曰。子之言然。抑吾尝辱知于公。公之恬与介。非仅一节而已。虽不自恤其贫。而未尝不恤民之穷也。虽不自安于宠命。而未尝不思所以报主也。苟恤民之穷。而思所以报主。则公必无让。既而公果行。不佞于是叹曰。北方之士。则诚
如人。不佞曰。吾尝辱知于公矣。公以经术文章进。致官至太学士。性恬而行介。家贫无甔石不恤。遇有宠命。辄逡逡不自安。辞未卒。士耸然而喜。既而悄然有忧色。不佞曰。吾为子语监司之贤。子北方之士也。其喜固也。其有忧色。何哉。士曰。吾乡之事棘矣。幸而得贤监司。民将有瘳。吾何以不喜。然公贫而不恤。又不自安于宠命。吾惧公之不来也。且夫吾乡之事棘矣。请言其一二。始吾乡并关南北为一省。监司专之。今峙而为二。又升兵马帅之号。几与监司埒。皆所以重边政。以安民也。然监司所治。仅十数郡县。操重而势分。凭高而施狭。凡符檄之所被。钤辖之所系。往往龃龉而不相合。捍格而不相通。比岁为监司者多患之。公则如之何。前有使者至吾乡。悉取无名之税。与夫官吏之谬袭者。痛革之。其间。亦有矫而过者。行之而难乎继。然民既惠之。监司不能改为也。苟为之。而复如初。则民不支。遂以行之。则官吏又以病告。公则如之何。米粟之迁于外者。防则无以善于邻。不防则五谷之直日踊。而民无所得食。金宝之出于中者。止则无以裕于国。不止则四方奸利之徒日萃。而山川不堪其椎凿。公则又如之何。不佞曰。子之言然。抑吾尝辱知于公。公之恬与介。非仅一节而已。虽不自恤其贫。而未尝不恤民之穷也。虽不自安于宠命。而未尝不思所以报主也。苟恤民之穷。而思所以报主。则公必无让。既而公果行。不佞于是叹曰。北方之士。则诚明美堂集卷九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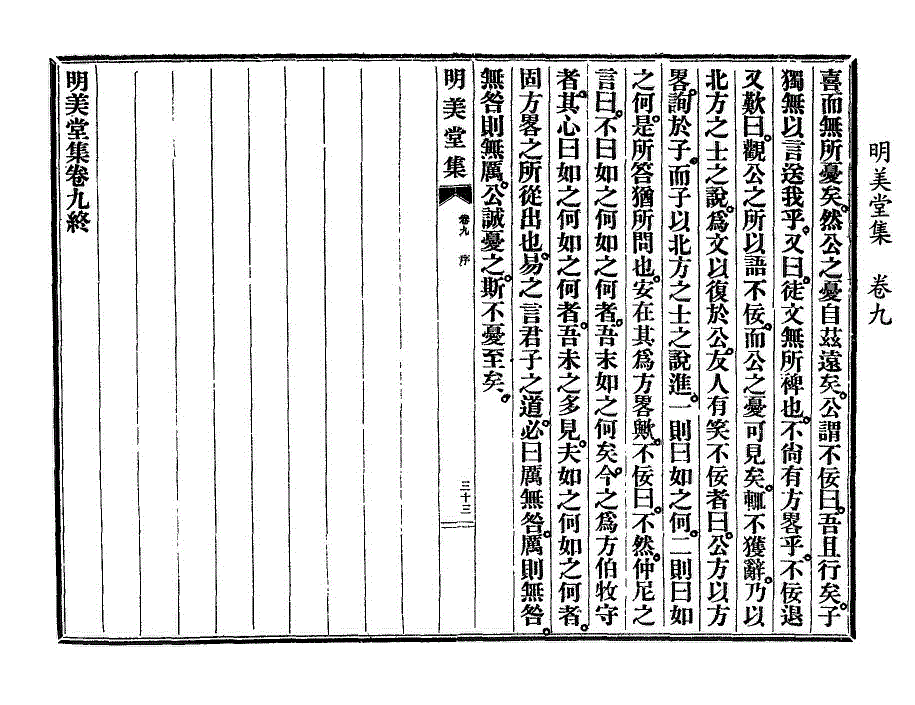 喜而无所忧矣。然公之忧自兹远矣。公谓不佞曰。吾且行矣。子独无以言送我乎。又曰。徒文无所裨也。不尚有方略乎。不佞退又叹曰。观公之所以语不佞。而公之忧可见矣。辄不获辞。乃以北方之士之说。为文以复于公。友人有笑不佞者曰。公方以方略。询于子。而子以北方之士之说进。一则曰如之何。二则曰如之何。是所答犹所问也。安在其为方略欤。不佞曰。不然。仲尼之言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矣。今之为方伯牧守者。其心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之多见。夫如之何如之何者。固方略之所从出也。易之言君子之道。必曰厉无咎。厉则无咎。无咎则无厉。公诚忧之。斯不忧至矣。
喜而无所忧矣。然公之忧自兹远矣。公谓不佞曰。吾且行矣。子独无以言送我乎。又曰。徒文无所裨也。不尚有方略乎。不佞退又叹曰。观公之所以语不佞。而公之忧可见矣。辄不获辞。乃以北方之士之说。为文以复于公。友人有笑不佞者曰。公方以方略。询于子。而子以北方之士之说进。一则曰如之何。二则曰如之何。是所答犹所问也。安在其为方略欤。不佞曰。不然。仲尼之言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矣。今之为方伯牧守者。其心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之多见。夫如之何如之何者。固方略之所从出也。易之言君子之道。必曰厉无咎。厉则无咎。无咎则无厉。公诚忧之。斯不忧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