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霁轩集卷之三 第 x 页
霁轩集卷之三
题跋
题跋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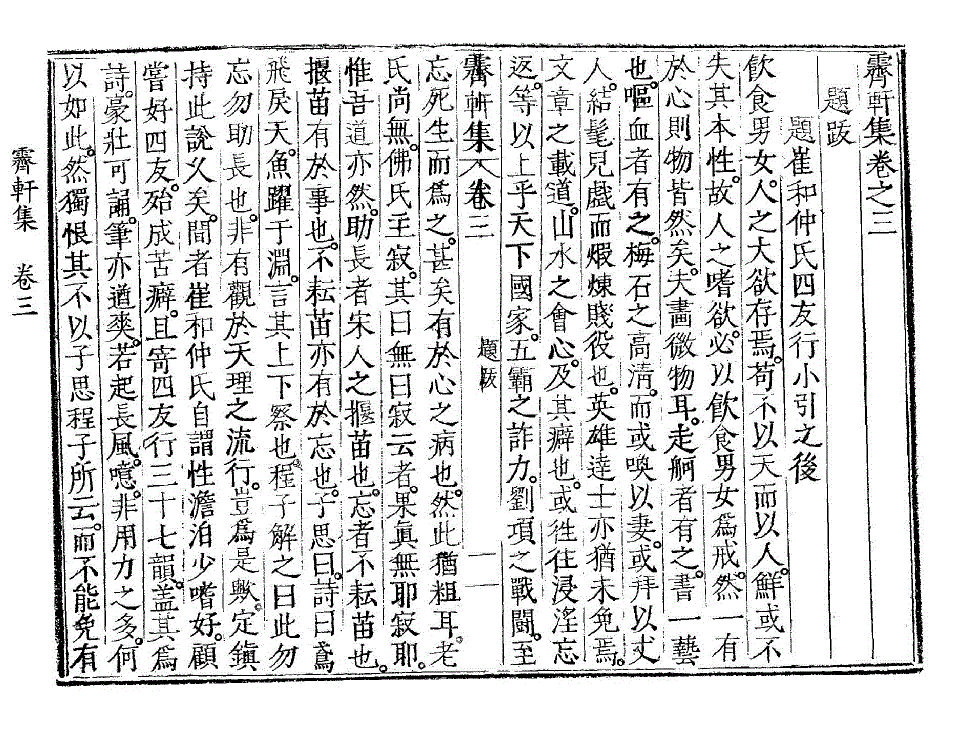 题崔和仲氏四友行小引之后
题崔和仲氏四友行小引之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苟不以天而以人。鲜或不失其本性。故人之嗜欲。必以饮食男女为戒。然一有于心则物皆然矣。夫画微物耳。走舸者有之。书一艺也。呕血者有之。梅石之高清。而或唤以妻。或拜以丈人。结髦儿戏而煅炼贱役也。英雄达士亦犹未免焉。文章之载道。山水之会心。及其癖也。或往往浸淫忘返。等以上乎天下国家。五霸之诈力。刘项之战斗。至忘死生而为之。甚矣有于心之病也。然此犹粗耳。老氏尚无。佛氏主寂。其曰无曰寂云者。果真无耶寂耶。惟吾道亦然。助长者宋人之揠苗也。忘者不耘苗也。揠苗有于事也。不耘苗亦有于忘也。子思曰。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程子解之曰此勿忘勿助长也。非有观于天理之流行。岂为是欤。定镇持此说久矣。间者崔和仲氏自谓性澹泊少嗜好。顾尝好四友。殆成苦癖。且寄四友行三十七韵。盖其为诗。豪壮可诵。笔亦遒爽。若起长风。噫。非用力之多。何以如此。然独恨其不以子思程子所云。而不能免有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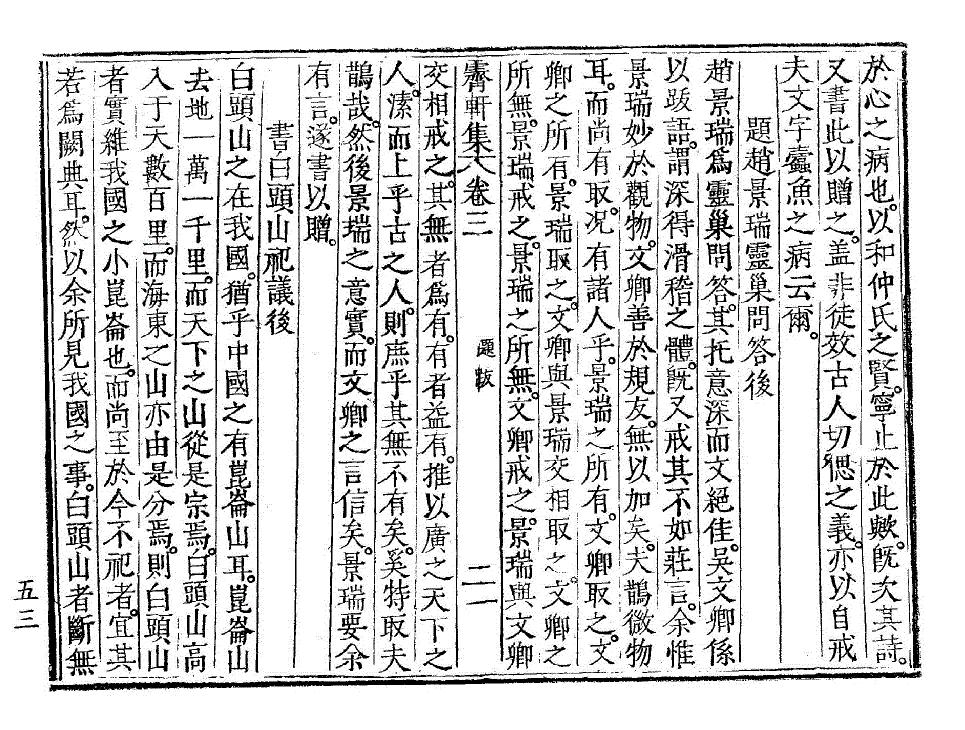 于心之病也。以和仲氏之贤。宁止于此欤。既次其诗。又书此以赠之。盖非徒效古人切偲之义。亦以自戒夫文字蠹鱼之病云尔。
于心之病也。以和仲氏之贤。宁止于此欤。既次其诗。又书此以赠之。盖非徒效古人切偲之义。亦以自戒夫文字蠹鱼之病云尔。题赵景瑞灵巢问答后
赵景瑞为灵巢问答。其托意深而文绝佳。吴文卿系以跋语。谓深得滑稽之体。既又戒其不如庄言。余惟景瑞妙于观物。文卿善于规友。无以加矣。夫鹊微物耳。而尚有取。况有诸人乎。景瑞之所有。文卿取之。文卿之所有。景瑞取之。文卿与景瑞交相取之。文卿之所无。景瑞戒之。景瑞之所无。文卿戒之。景瑞与文卿交相戒之。其无者为有。有者益有。推以广之天下之人。溸而上乎古之人。则庶乎其无不有矣。奚特取夫鹊哉。然后景瑞之意实。而文卿之言信矣。景瑞要余有言。遂书以赠。
书白头山祀议后
白头山之在我国。犹乎中国之有昆崙山耳。昆崙山去地一万一千里。而天下之山从是宗焉。白头山高入于天数百里。而海东之山亦由是分焉。则白头山者实维我国之小昆崙也。而尚至于今不祀者。宜其若为阙典耳。然以余所见我国之事。白头山者断无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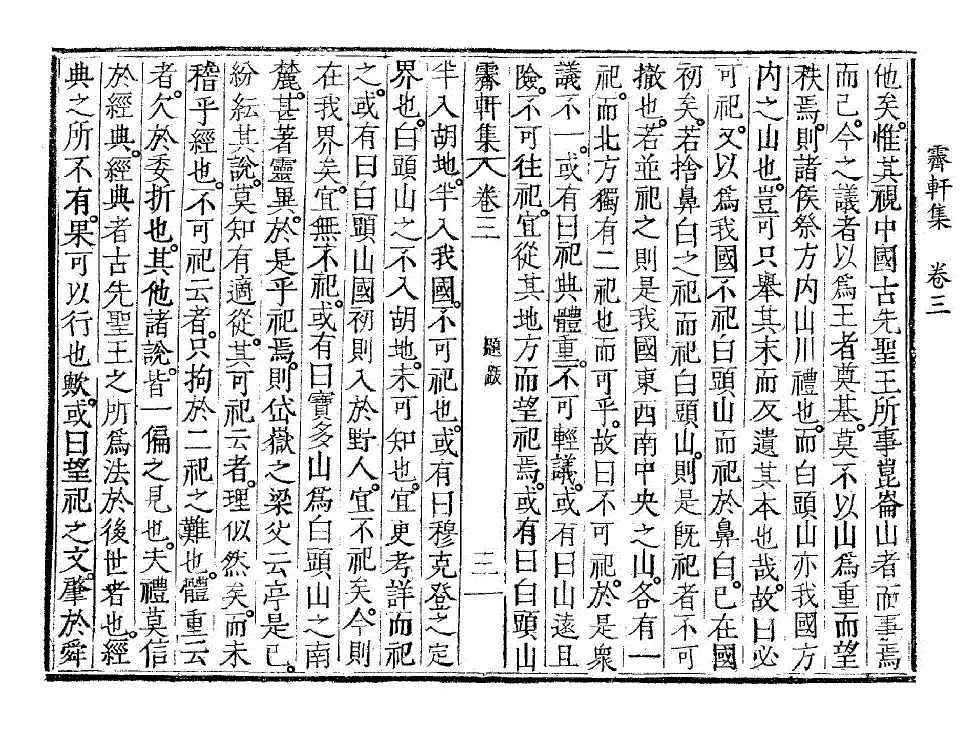 他矣。惟其视中国古先圣王所事昆崙山者而事焉而已。今之议者以为王者奠基。莫不以山为重而望秩焉。则诸侯祭方内山川礼也。而白头山亦我国方内之山也。岂可只举其末而反遗其本也哉。故曰必可祀。又以为我国不祀白头山而祀于鼻白。已在国初矣。若舍鼻白之祀而祀白头山。则是既祀者不可撤也。若并祀之则是我国东西南中央之山。各有一祀。而北方独有二祀也而可乎。故曰不可祀。于是众议不一。或有曰祀典体重。不可轻议。或有曰山远且险。不可往祀。宜从其地方而望祀焉。或有曰白头山半入胡地。半入我国。不可祀也。或有曰穆克登之定界也。白头山之不入胡地。未可知也。宜更考详而祀之。或有曰白头山国初则入于野人。宜不祀矣。今则在我界矣。宜无不祀。或有曰宝多山为白头山之南麓。甚著灵异。于是乎祀焉。则岱岳之梁父云亭是已。纷纭其说。莫知有适从。其可祀云者。理似然矣。而未稽乎经也。不可祀云者。只拘于二祀之难也。体重云者。欠于委折也。其他诸说。皆一偏之见也。夫礼莫信于经典。经典者古先圣王之所为法于后世者也。经典之所不有。果可以行也欤。或曰望祀之文。肇于舜
他矣。惟其视中国古先圣王所事昆崙山者而事焉而已。今之议者以为王者奠基。莫不以山为重而望秩焉。则诸侯祭方内山川礼也。而白头山亦我国方内之山也。岂可只举其末而反遗其本也哉。故曰必可祀。又以为我国不祀白头山而祀于鼻白。已在国初矣。若舍鼻白之祀而祀白头山。则是既祀者不可撤也。若并祀之则是我国东西南中央之山。各有一祀。而北方独有二祀也而可乎。故曰不可祀。于是众议不一。或有曰祀典体重。不可轻议。或有曰山远且险。不可往祀。宜从其地方而望祀焉。或有曰白头山半入胡地。半入我国。不可祀也。或有曰穆克登之定界也。白头山之不入胡地。未可知也。宜更考详而祀之。或有曰白头山国初则入于野人。宜不祀矣。今则在我界矣。宜无不祀。或有曰宝多山为白头山之南麓。甚著灵异。于是乎祀焉。则岱岳之梁父云亭是已。纷纭其说。莫知有适从。其可祀云者。理似然矣。而未稽乎经也。不可祀云者。只拘于二祀之难也。体重云者。欠于委折也。其他诸说。皆一偏之见也。夫礼莫信于经典。经典者古先圣王之所为法于后世者也。经典之所不有。果可以行也欤。或曰望祀之文。肇于舜霁轩集卷之三 第 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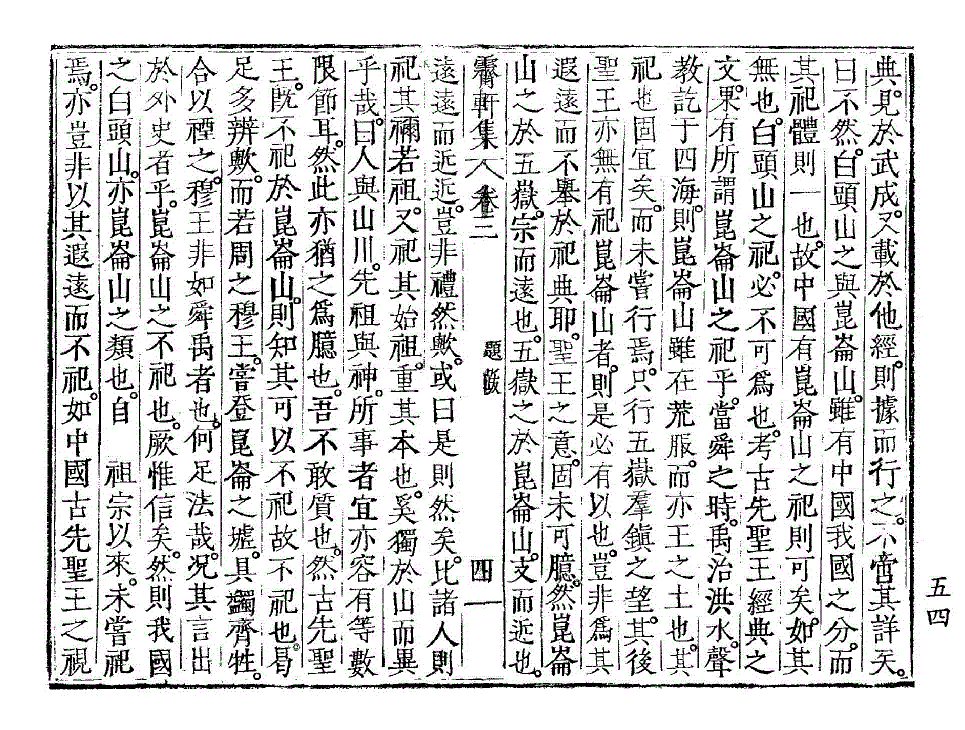 典。见于武成。又载于他经。则据而行之。不啻其详矣。曰不然。白头山之与昆崙山。虽有中国我国之分。而其祀体则一也。故中国有昆崙山之祀则可矣。如其无也。白头山之祀。必不可为也。考古先圣王经典之文。果有所谓昆崙山之祀乎。当舜之时。禹治洪水。声教讫于四海。则昆崙山虽在荒服。而亦王之土也。其祀也固宜矣。而未尝行焉。只行五岳群镇之望。其后圣王亦无有祀昆崙山者。则是必有以也。岂非为其遐远而不举于祀典耶。圣王之意。固未可臆。然昆崙山之于五岳。宗而远也。五岳之于昆崙山。支而近也。远远而近近。岂非礼然欤。或曰是则然矣。比诸人则祀其祢若祖。又祀其始祖。重其本也。奚独于山而异乎哉。曰人与山川。先祖与神。所事者宜亦容有等数限节耳。然此亦犹之为臆也。吾不敢质也。然古先圣王。既不祀于昆崙山。则知其可以不祀故不祀也。曷足多辨欤。而若周之穆王。尝登昆崙之墟。具蠲齐牲。合以禋之。穆王非如舜禹者也。何足法哉。况其言出于外史者乎。昆崙山之不祀也。厥惟信矣。然则我国之白头山。亦昆崙山之类也。自 祖宗以来。未尝祀焉。亦岂非以其遐远而不祀。如中国古先圣王之视
典。见于武成。又载于他经。则据而行之。不啻其详矣。曰不然。白头山之与昆崙山。虽有中国我国之分。而其祀体则一也。故中国有昆崙山之祀则可矣。如其无也。白头山之祀。必不可为也。考古先圣王经典之文。果有所谓昆崙山之祀乎。当舜之时。禹治洪水。声教讫于四海。则昆崙山虽在荒服。而亦王之土也。其祀也固宜矣。而未尝行焉。只行五岳群镇之望。其后圣王亦无有祀昆崙山者。则是必有以也。岂非为其遐远而不举于祀典耶。圣王之意。固未可臆。然昆崙山之于五岳。宗而远也。五岳之于昆崙山。支而近也。远远而近近。岂非礼然欤。或曰是则然矣。比诸人则祀其祢若祖。又祀其始祖。重其本也。奚独于山而异乎哉。曰人与山川。先祖与神。所事者宜亦容有等数限节耳。然此亦犹之为臆也。吾不敢质也。然古先圣王。既不祀于昆崙山。则知其可以不祀故不祀也。曷足多辨欤。而若周之穆王。尝登昆崙之墟。具蠲齐牲。合以禋之。穆王非如舜禹者也。何足法哉。况其言出于外史者乎。昆崙山之不祀也。厥惟信矣。然则我国之白头山。亦昆崙山之类也。自 祖宗以来。未尝祀焉。亦岂非以其遐远而不祀。如中国古先圣王之视霁轩集卷之三 第 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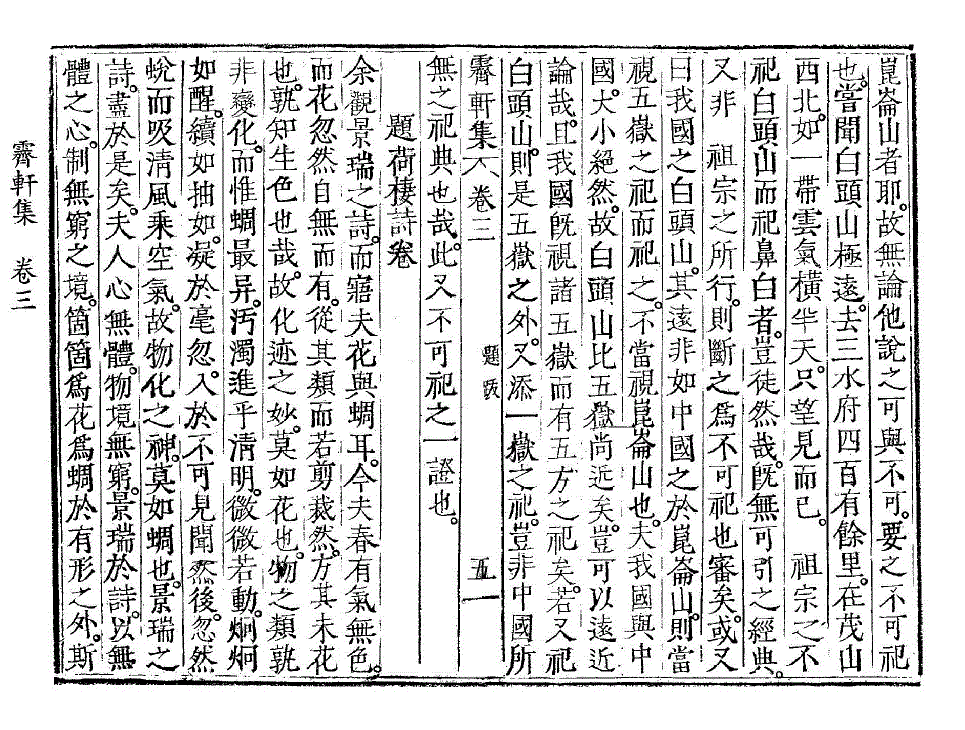 昆崙山者耶。故无论他说之可与不可。要之不可祀也。尝闻白头山极远。去三水府四百有馀里。在茂山西北。如一带云气横半天。只望见而已。 祖宗之不祀白头山而祀鼻白者。岂徒然哉。既无可引之经典。又非 祖宗之所行。则断之为不可祀也审矣。或又曰我国之白头山。其远非如中国之于昆崙山。则当视五岳之祀而祀之。不当视昆崙山也。夫我国与中国。大小绝然。故白头山比五岳尚近矣。岂可以远近论哉。且我国既视诸五岳而有五方之祀矣。若又祀白头山。则是五岳之外。又添一岳之祀。岂非中国所无之祀典也哉。此又不可祀之一證也。
昆崙山者耶。故无论他说之可与不可。要之不可祀也。尝闻白头山极远。去三水府四百有馀里。在茂山西北。如一带云气横半天。只望见而已。 祖宗之不祀白头山而祀鼻白者。岂徒然哉。既无可引之经典。又非 祖宗之所行。则断之为不可祀也审矣。或又曰我国之白头山。其远非如中国之于昆崙山。则当视五岳之祀而祀之。不当视昆崙山也。夫我国与中国。大小绝然。故白头山比五岳尚近矣。岂可以远近论哉。且我国既视诸五岳而有五方之祀矣。若又祀白头山。则是五岳之外。又添一岳之祀。岂非中国所无之祀典也哉。此又不可祀之一證也。题荷栖诗卷
余观景瑞之诗。而寤夫花与蜩耳。今夫春有气无色。而花忽然自无而有。从其类而若剪裁然。方其未花也。孰知生色也哉。故化迹之妙。莫如花也。物之类孰非变化。而惟蜩最异。污浊进乎清明。微微若动。炯炯如醒。续如抽如。凝于毫忽。入于不可见闻然后。忽然蜕而吸清风乘空气。故物化之神。莫如蜩也。景瑞之诗。尽于是矣。夫人心无体。物境无穷。景瑞于诗。以无体之心。制无穷之境。个个为花为蜩于有形之外。斯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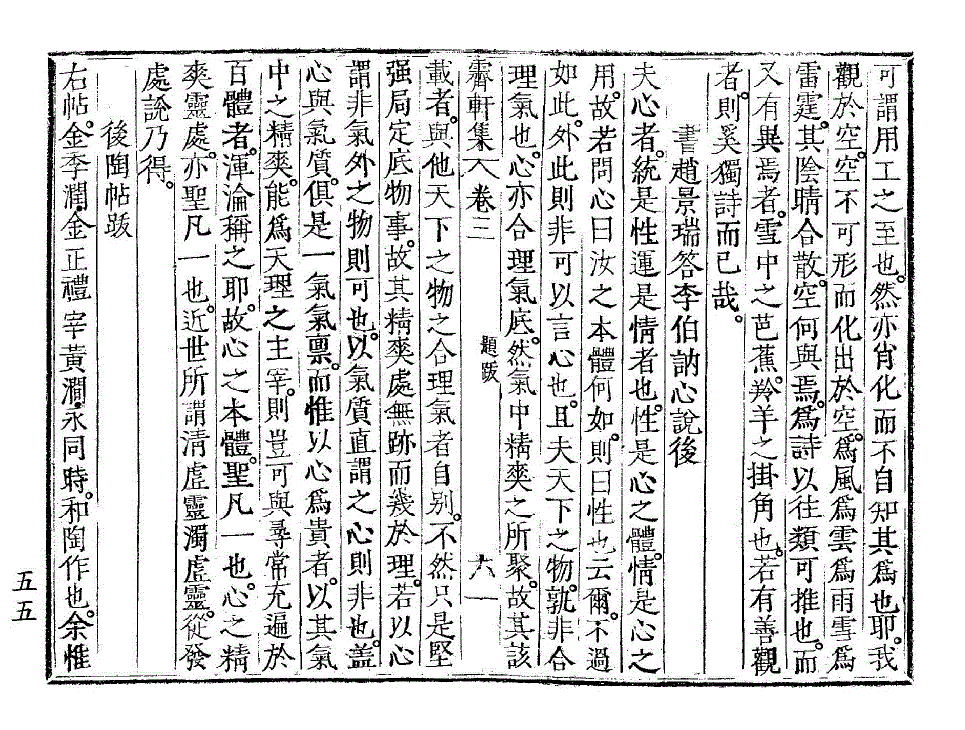 可谓用工之至也。然亦肖化而不自知其为也耶。我观于空。空不可形而化出于空。为风为云为雨雪为雷霆。其阴晴合散。空何与焉。为诗以往类可推也。而又有异焉者。雪中之芭蕉。羚羊之挂角也。若有善观者。则奚独诗而已哉。
可谓用工之至也。然亦肖化而不自知其为也耶。我观于空。空不可形而化出于空。为风为云为雨雪为雷霆。其阴晴合散。空何与焉。为诗以往类可推也。而又有异焉者。雪中之芭蕉。羚羊之挂角也。若有善观者。则奚独诗而已哉。书赵景瑞答李伯讷心说后
夫心者。统是性运是情者也。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故若问心曰汝之本体何如。则曰性也云尔。不过如此。外此则非可以言心也。且夫天下之物。孰非合理气也。心亦合理气底。然气中精爽之所聚。故其该载者。与他天下之物之合理气者自别。不然只是坚强局定底物事。故其精爽处无迹而几于理。若以心谓非气外之物则可也。以气质直谓之心则非也。盖心与气质。俱是一气气禀。而惟以心为贵者。以其气中之精爽。能为天理之主宰。则岂可与寻常充遍于百体者。浑沦称之耶。故心之本体。圣凡一也。心之精爽灵处。亦圣凡一也。近世所谓清虚灵浊虚灵。从发处说乃得。
后陶帖跋
右帖。金季润,金正礼宰黄涧,永同时。和陶作也。余惟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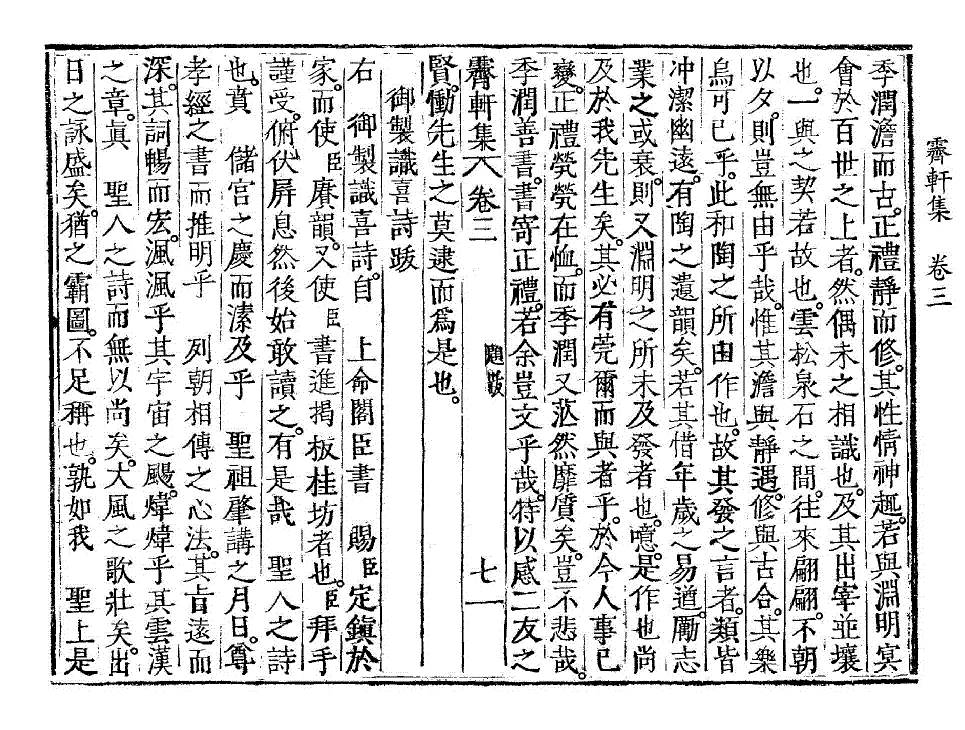 季润澹而古。正礼静而修。其性情神趣。若与渊明冥会于百世之上者。然偶未之相识也。及其出宰并壤也。一与之契若故也。云松泉石之间。往来翩翩。不朝以夕。则岂无由乎哉。惟其澹与静遇。修与古合。其乐乌可已乎。此和陶之所由作也。故其发之言者。类皆冲洁幽远。有陶之遗韵矣。若其惜年岁之易遒。励志业之或衰。则又渊明之所未及发者也。噫。是作也尚及于我先生矣。其必有莞尔而与者乎。于今人事已变。正礼茕茕在恤。而季润又茫然靡质矣。岂不悲哉。季润善书。书寄正礼。若余岂文乎哉。特以感二友之贤。恸先生之莫逮而为是也。
季润澹而古。正礼静而修。其性情神趣。若与渊明冥会于百世之上者。然偶未之相识也。及其出宰并壤也。一与之契若故也。云松泉石之间。往来翩翩。不朝以夕。则岂无由乎哉。惟其澹与静遇。修与古合。其乐乌可已乎。此和陶之所由作也。故其发之言者。类皆冲洁幽远。有陶之遗韵矣。若其惜年岁之易遒。励志业之或衰。则又渊明之所未及发者也。噫。是作也尚及于我先生矣。其必有莞尔而与者乎。于今人事已变。正礼茕茕在恤。而季润又茫然靡质矣。岂不悲哉。季润善书。书寄正礼。若余岂文乎哉。特以感二友之贤。恸先生之莫逮而为是也。御制识喜诗跋
右 御制识喜诗。自 上命阁臣书 赐臣定镇于家。而使臣赓韵。又使臣书进揭板桂坊者也。臣拜手谨受。俯伏屏息然后始敢读之。有是哉 圣人之诗也。贲 储宫之庆而溸及乎 圣祖肇讲之月日。尊孝经之书而推明乎 列朝相传之心法。其旨远而深。其词畅而宏。沨沨乎其宇宙之飏。炜炜乎其云汉之章。真 圣人之诗而无以尚矣。大风之歌壮矣。出日之咏盛矣。犹之霸图。不足称也。孰如我 圣上是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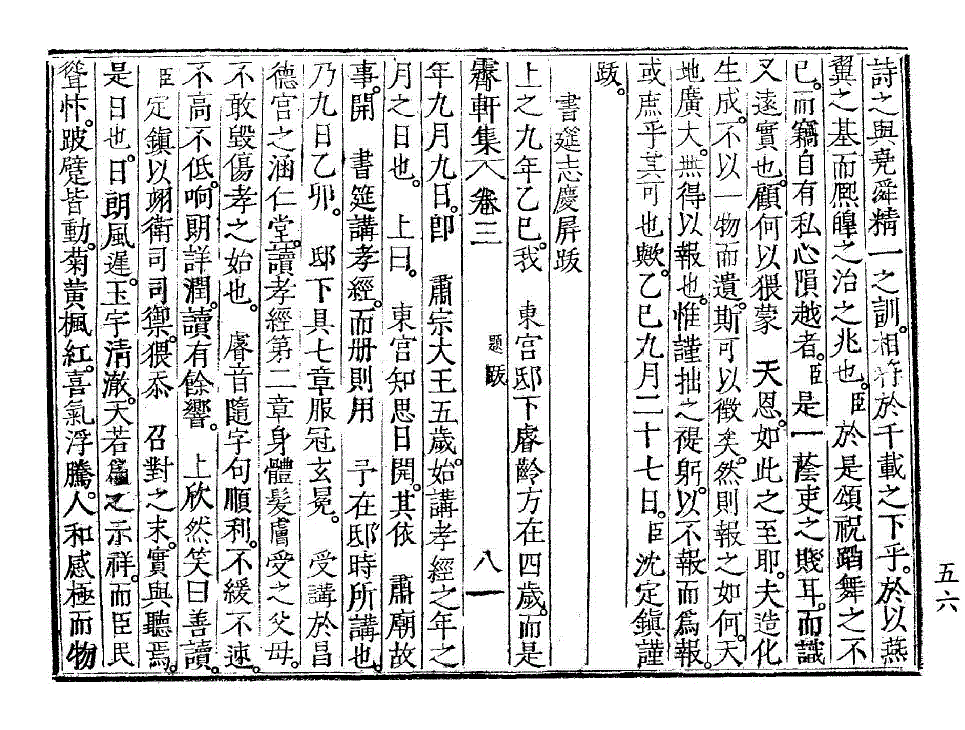 诗之与尧舜精一之训。相符于千载之下乎。于以燕翼之基而熙皞之治之兆也。臣于是颂祝蹈舞之不已。而窃自有私心陨越者。臣是一荫吏之贱耳。而识又远实也。顾何以猥蒙 天恩。如此之至耶。夫造化生成。不以一物而遗。斯可以徵矣。然则报之如何。天地广大。无得以报也。惟谨拙之禔躬。以不报而为报。或庶乎其可也欤。乙巳九月二十七日。臣沈定镇谨跋。
诗之与尧舜精一之训。相符于千载之下乎。于以燕翼之基而熙皞之治之兆也。臣于是颂祝蹈舞之不已。而窃自有私心陨越者。臣是一荫吏之贱耳。而识又远实也。顾何以猥蒙 天恩。如此之至耶。夫造化生成。不以一物而遗。斯可以徵矣。然则报之如何。天地广大。无得以报也。惟谨拙之禔躬。以不报而为报。或庶乎其可也欤。乙巳九月二十七日。臣沈定镇谨跋。书筵志庆屏跋
上之九年乙巳。我 东宫邸下睿龄方在四岁。而是年九月九日。即 肃宗大王五岁。始讲孝经之年之月之日也。 上曰。 东宫知思日开。其依 肃庙故事。开 书筵讲孝经。而册则用 予在邸时所讲也。乃九日乙卯。 邸下具七章服冠玄冕。 受讲于昌德宫之涵仁堂。读孝经第二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睿音随字句顺利。不缓不速。不高不低。响朗详润。读有馀响。 上欣然笑曰善读。臣定镇以翊卫司司御。猥忝 召对之末。实与听焉。是日也。日朗风迟。玉宇清澈。天若为之示祥。而臣民耸忭。跛躄皆动。菊黄枫红。喜气浮腾。人和感极而物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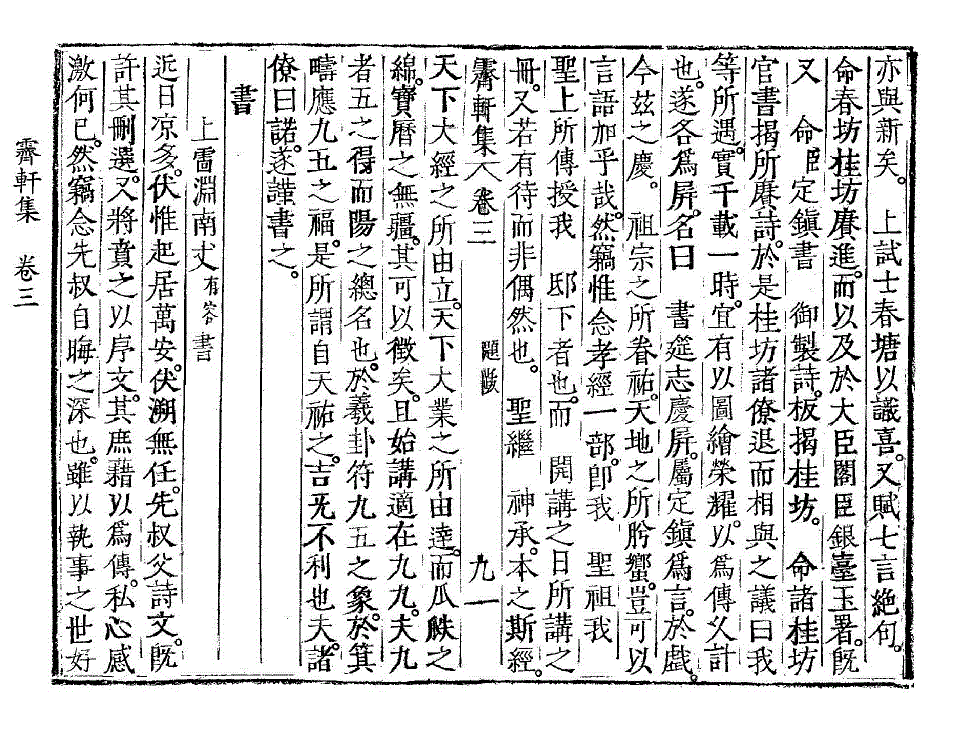 亦与新矣。 上试士春塘以识喜。又赋七言绝句。 命春坊桂坊赓进。而以及于大臣阁臣银台玉署。既又 命臣定镇书 御制诗。板揭桂坊。 命诸桂坊官书揭所赓诗。于是桂坊诸僚退而相与之议曰我等所遇。实千载一时。宜有以图绘荣耀。以为传久计也。遂各为屏。名曰 书筵志庆屏。属定镇为言。于戏。今玆之庆。 祖宗之所眷祐。天地之所肸蚃。岂可以言语加乎哉。然窃惟念孝经一部。即我 圣祖我 圣上所传授我 邸下者也。而 开讲之日所讲之册。又若有待而非偶然也。 圣继 神承。本之斯经。天下大经之所由立。天下大业之所由达。而瓜瓞之绵。宝历之无疆。其可以徵矣。且始讲适在九九。夫九者五之得而阳之总名也。于羲卦符九五之象。于箕畴应九五之福。是所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诸僚曰诺。遂谨书之。
亦与新矣。 上试士春塘以识喜。又赋七言绝句。 命春坊桂坊赓进。而以及于大臣阁臣银台玉署。既又 命臣定镇书 御制诗。板揭桂坊。 命诸桂坊官书揭所赓诗。于是桂坊诸僚退而相与之议曰我等所遇。实千载一时。宜有以图绘荣耀。以为传久计也。遂各为屏。名曰 书筵志庆屏。属定镇为言。于戏。今玆之庆。 祖宗之所眷祐。天地之所肸蚃。岂可以言语加乎哉。然窃惟念孝经一部。即我 圣祖我 圣上所传授我 邸下者也。而 开讲之日所讲之册。又若有待而非偶然也。 圣继 神承。本之斯经。天下大经之所由立。天下大业之所由达。而瓜瓞之绵。宝历之无疆。其可以徵矣。且始讲适在九九。夫九者五之得而阳之总名也。于羲卦符九五之象。于箕畴应九五之福。是所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诸僚曰诺。遂谨书之。霁轩集卷之三
书
上䨓渊南丈(有容)书
近日凉多。伏惟起居万安。伏溯无任。先叔父诗文。既许其删选。又将贲之以序文。其庶藉以为传。私心感激何已。然窃念先叔自晦之深也。虽以执事之世好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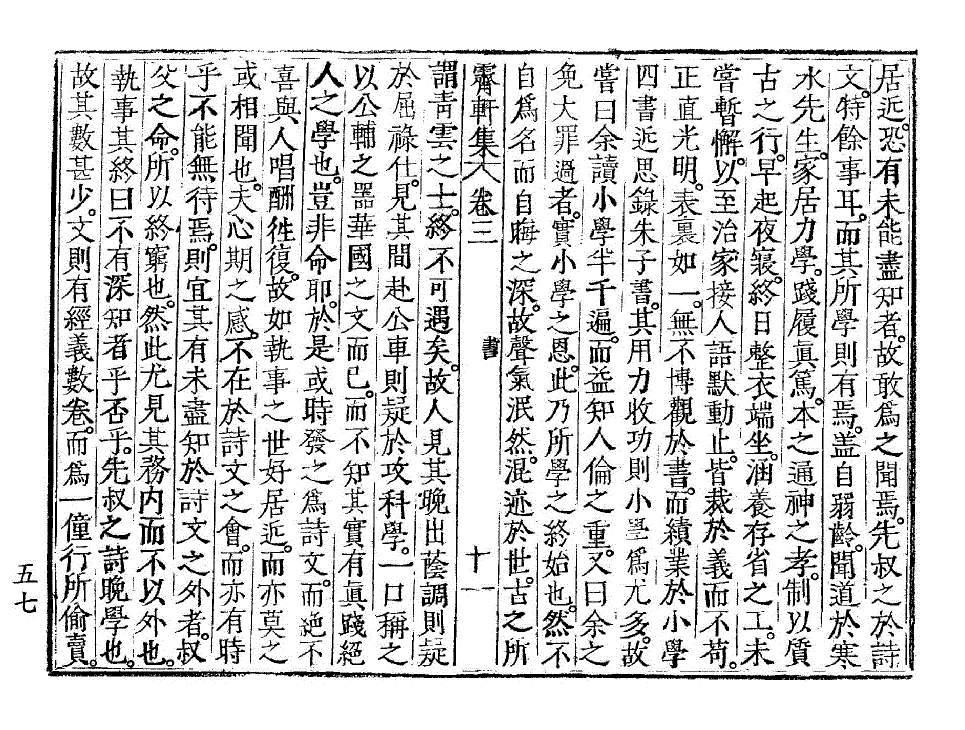 居近。恐有未能尽知者。故敢为之闻焉。先叔之于诗文。特馀事耳。而其所学则有焉。盖自弱龄。闻道于寒水先生。家居力学。践履真笃。本之通神之孝。制以质古之行。早起夜寝。终日整衣端坐。涵养存省之工。未尝暂懈。以至治家接人语默动止。皆裁于义而不苟。正直光明。表里如一。无不博观于书。而绩业于小学四书近思录朱子书。其用力收功则小学为尤多。故尝曰余读小学半千遍。而益知人伦之重。又曰余之免大罪过者。实小学之恩。此乃所学之终始也。然不自为名而自晦之深。故声气泯然。混迹于世。古之所谓青云之士。终不可遇矣。故人见其晚出荫调则疑于屈禄仕。见其间赴公车则疑于攻科学。一口称之以公辅之器华国之文而已。而不知其实有真践绝人之学也。岂非命耶。于是或时发之为诗文。而绝不喜与人唱酬往复。故如执事之世好居近。而亦莫之或相闻也。夫心期之感。不在于诗文之会。而亦有时乎不能无待焉。则宜其有未尽知于诗文之外者。叔父之命。所以终穷也。然此尤见其务内而不以外也。执事其终曰不有深知者乎否乎。先叔之诗晚学也。故其数甚少。文则有经义数卷。而为一僮行所偷卖。
居近。恐有未能尽知者。故敢为之闻焉。先叔之于诗文。特馀事耳。而其所学则有焉。盖自弱龄。闻道于寒水先生。家居力学。践履真笃。本之通神之孝。制以质古之行。早起夜寝。终日整衣端坐。涵养存省之工。未尝暂懈。以至治家接人语默动止。皆裁于义而不苟。正直光明。表里如一。无不博观于书。而绩业于小学四书近思录朱子书。其用力收功则小学为尤多。故尝曰余读小学半千遍。而益知人伦之重。又曰余之免大罪过者。实小学之恩。此乃所学之终始也。然不自为名而自晦之深。故声气泯然。混迹于世。古之所谓青云之士。终不可遇矣。故人见其晚出荫调则疑于屈禄仕。见其间赴公车则疑于攻科学。一口称之以公辅之器华国之文而已。而不知其实有真践绝人之学也。岂非命耶。于是或时发之为诗文。而绝不喜与人唱酬往复。故如执事之世好居近。而亦莫之或相闻也。夫心期之感。不在于诗文之会。而亦有时乎不能无待焉。则宜其有未尽知于诗文之外者。叔父之命。所以终穷也。然此尤见其务内而不以外也。执事其终曰不有深知者乎否乎。先叔之诗晚学也。故其数甚少。文则有经义数卷。而为一僮行所偷卖。霁轩集卷之三 第 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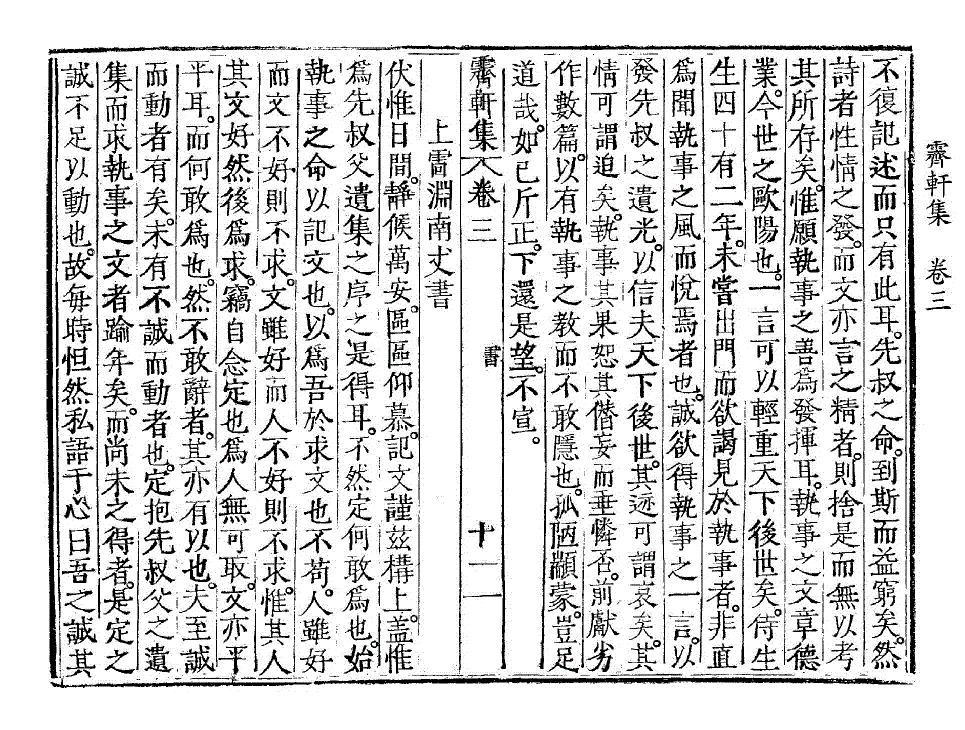 不复记述而只有此耳。先叔之命。到斯而益穷矣。然诗者性情之发。而文亦言之精者。则舍是而无以考其所存矣。惟愿执事之善为发挥耳。执事之文章德业。今世之欧阳也。一言可以轻重天下后世矣。侍生生四十有二年。未尝出门而欲谒见于执事者。非直为闻执事之风而悦焉者也。诚欲得执事之一言。以发先叔之遗光。以信夫天下后世。其迹可谓哀矣。其情可谓迫矣。执事其果恕其僭妄而垂怜否。前献劣作数篇。以有执事之教而不敢隐也。孤陋颛蒙。岂足道哉。如己斤正。下还是望。不宣。
不复记述而只有此耳。先叔之命。到斯而益穷矣。然诗者性情之发。而文亦言之精者。则舍是而无以考其所存矣。惟愿执事之善为发挥耳。执事之文章德业。今世之欧阳也。一言可以轻重天下后世矣。侍生生四十有二年。未尝出门而欲谒见于执事者。非直为闻执事之风而悦焉者也。诚欲得执事之一言。以发先叔之遗光。以信夫天下后世。其迹可谓哀矣。其情可谓迫矣。执事其果恕其僭妄而垂怜否。前献劣作数篇。以有执事之教而不敢隐也。孤陋颛蒙。岂足道哉。如己斤正。下还是望。不宣。上䨓渊南丈书
伏惟日间。静候万安。区区仰慕。记文谨玆构上。盖惟为先叔父遗集之序之是得耳。不然定何敢为也。始执事之命以记文也。以为吾于求文也不苟。人虽好而文不好则不求。文虽好而人不好则不求。惟其人其文好然后为求。窃自念定也为人无可取。文亦平平耳。而何敢为也。然不敢辞者。其亦有以也。夫至诚而动者有矣。未有不诚而动者也。定抱先叔父之遗集而求执事之文者踰年矣。而尚未之得者。是定之诚不足以动也。故每时怛然私语于心曰吾之诚其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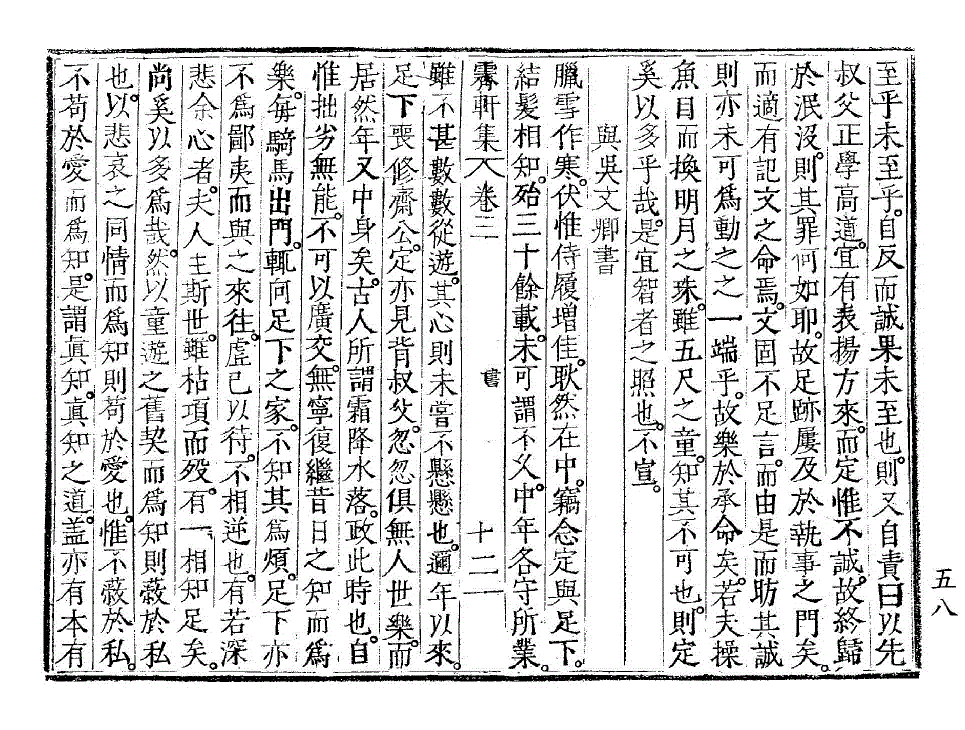 至乎未至乎。自反而诚果未至也。则又自责曰以先叔父正学高道。宜有表扬方来。而定惟不诚。故终归于泯没。则其罪何如耶。故足迹屡及于执事之门矣。而适有记文之命焉。文固不足言。而由是而昉其诚则亦未可为动之之一端乎。故乐于承命矣。若夫操鱼目而换明月之珠。虽五尺之童。知其不可也。则定奚以多乎哉。是宜智者之照也。不宣。
至乎未至乎。自反而诚果未至也。则又自责曰以先叔父正学高道。宜有表扬方来。而定惟不诚。故终归于泯没。则其罪何如耶。故足迹屡及于执事之门矣。而适有记文之命焉。文固不足言。而由是而昉其诚则亦未可为动之之一端乎。故乐于承命矣。若夫操鱼目而换明月之珠。虽五尺之童。知其不可也。则定奚以多乎哉。是宜智者之照也。不宣。与吴文卿书
腊雪作寒。伏惟侍履增佳。耿然在中。窃念定与足下。结发相知。殆三十馀载。未可谓不久。中年各守所业。虽不甚数数从游。其心则未尝不悬悬也。迩年以来。足下丧修斋公。定亦见背叔父。忽忽俱无人世乐。而居然年又中身矣。古人所谓霜降水落。政此时也。自惟拙劣无能。不可以广交。无宁复继昔日之知而为乐。每骑马出门。辄向足下之家。不知其为烦。足下亦不为鄙夷而与之来往。虚己以待。不相逆也。有若深悲余心者。夫人主斯世。虽枯项而殁。有一相知足矣。尚奚以多为哉。然以童游之旧契而为知则蔽于私也。以悲哀之同情而为知则苟于爱也。惟不蔽于私。不苟于爱而为知。是谓真知。真知之道。盖亦有本有
霁轩集卷之三 第 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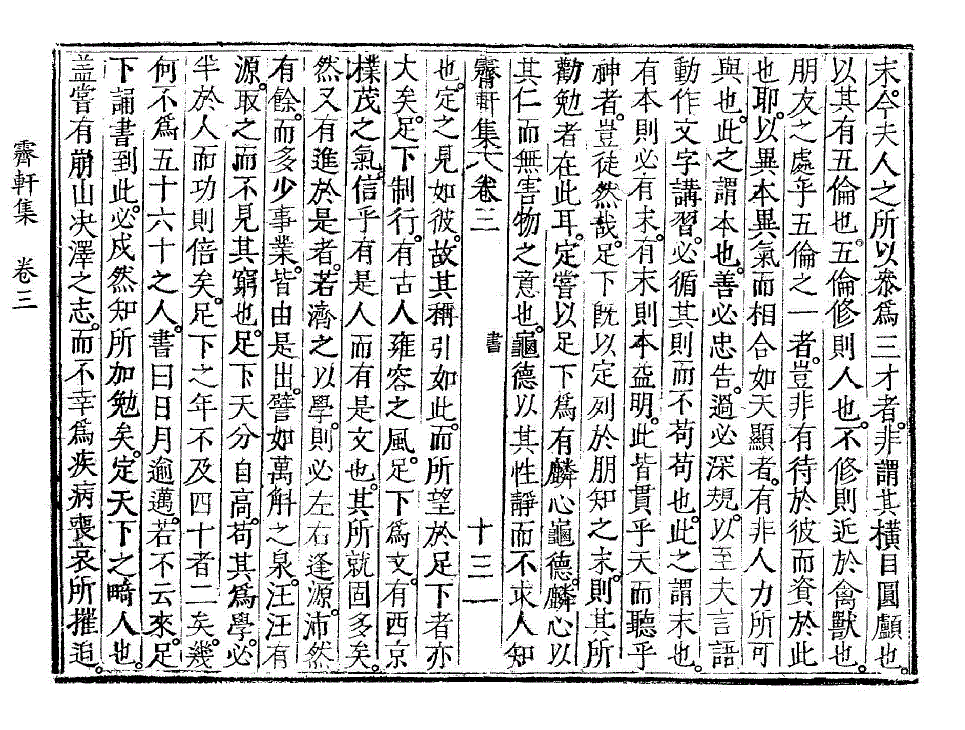 末。今夫人之所以参为三才者。非谓其横目圆颅也。以其有五伦也。五伦修则人也。不修则近于禽兽也。朋友之处乎五伦之一者。岂非有待于彼而资于此也耶。以异本异气而相合如天显者。有非人力所可与也。此之谓本也。善必忠告。过必深规。以至夫言语动作文字讲习。必循其则而不苟苟也。此之谓末也。有本则必有末。有末则本益明。此皆贯乎天而听乎神者。岂徒然哉。足下既以定列于朋知之末。则其所劝勉者在此耳。定尝以足下为有麟心龟德。麟心以其仁而无害物之意也。龟德以其性静而不求人知也。定之见如彼。故其称引如此。而所望于足下者亦大矣。足下制行。有古人雍容之风。足下为文。有西京朴茂之气。信乎有是人而有是文也。其所就固多矣。然又有进于是者。若济之以学。则必左右逢源。沛然有馀。而多少事业。皆由是出。譬如万斛之泉。汪汪有源。取之而不见其穷也。足下天分自高。苟其为学。必半于人而功则倍矣。足下之年不及四十者二矣。几何不为五十六十之人。书曰日月逾迈。若不云来。足下诵书到此。必戍然知所加勉矣。定天下之畸人也。盖尝有崩山决泽之志。而不幸为疾病丧哀所摧迫。
末。今夫人之所以参为三才者。非谓其横目圆颅也。以其有五伦也。五伦修则人也。不修则近于禽兽也。朋友之处乎五伦之一者。岂非有待于彼而资于此也耶。以异本异气而相合如天显者。有非人力所可与也。此之谓本也。善必忠告。过必深规。以至夫言语动作文字讲习。必循其则而不苟苟也。此之谓末也。有本则必有末。有末则本益明。此皆贯乎天而听乎神者。岂徒然哉。足下既以定列于朋知之末。则其所劝勉者在此耳。定尝以足下为有麟心龟德。麟心以其仁而无害物之意也。龟德以其性静而不求人知也。定之见如彼。故其称引如此。而所望于足下者亦大矣。足下制行。有古人雍容之风。足下为文。有西京朴茂之气。信乎有是人而有是文也。其所就固多矣。然又有进于是者。若济之以学。则必左右逢源。沛然有馀。而多少事业。皆由是出。譬如万斛之泉。汪汪有源。取之而不见其穷也。足下天分自高。苟其为学。必半于人而功则倍矣。足下之年不及四十者二矣。几何不为五十六十之人。书曰日月逾迈。若不云来。足下诵书到此。必戍然知所加勉矣。定天下之畸人也。盖尝有崩山决泽之志。而不幸为疾病丧哀所摧迫。霁轩集卷之三 第 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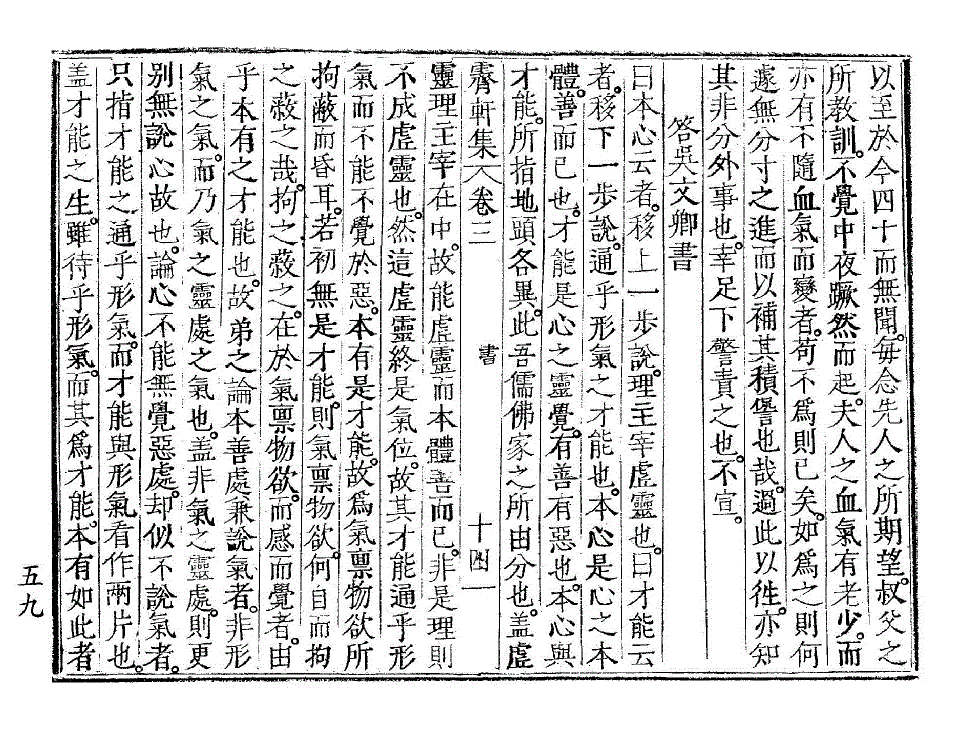 以至于今四十而无闻。每念先人之所期望。叔父之所教训。不觉中夜蹶然而起。夫人之血气有老少。而亦有不随血气而变者。苟不为则已矣。如为之则何遽无分寸之进而以补其积愆也哉。过此以往。亦知其非分外事也。幸足下警责之也。不宣。
以至于今四十而无闻。每念先人之所期望。叔父之所教训。不觉中夜蹶然而起。夫人之血气有老少。而亦有不随血气而变者。苟不为则已矣。如为之则何遽无分寸之进而以补其积愆也哉。过此以往。亦知其非分外事也。幸足下警责之也。不宣。答吴文卿书
曰本心云者。移上一步说。理主宰虚灵也。曰才能云者。移下一步说。通乎形气之才能也。本心是心之本体。善而已也。才能是心之灵觉。有善有恶也。本心与才能。所指地头各异。此吾儒佛家之所由分也。盖虚灵理主宰在中。故能虚灵而本体善而已。非是理则不成虚灵也。然这虚灵终是气位。故其才能通乎形气而不能不觉于恶。本有是才能。故为气禀物欲所拘蔽而昏耳。若初无是才能。则气禀物欲。何自而拘之蔽之哉。拘之蔽之。在于气禀物欲。而感而觉者。由乎本有之才能也。故弟之论本善处兼说气者。非形气之气。而乃气之灵处之气也。盖非气之灵处。则更别无说心故也。论心不能无觉恶处。却似不说气者。只指才能之通乎形气。而才能与形气看作两片也。盖才能之生。虽待乎形气。而其为才能。本有如此者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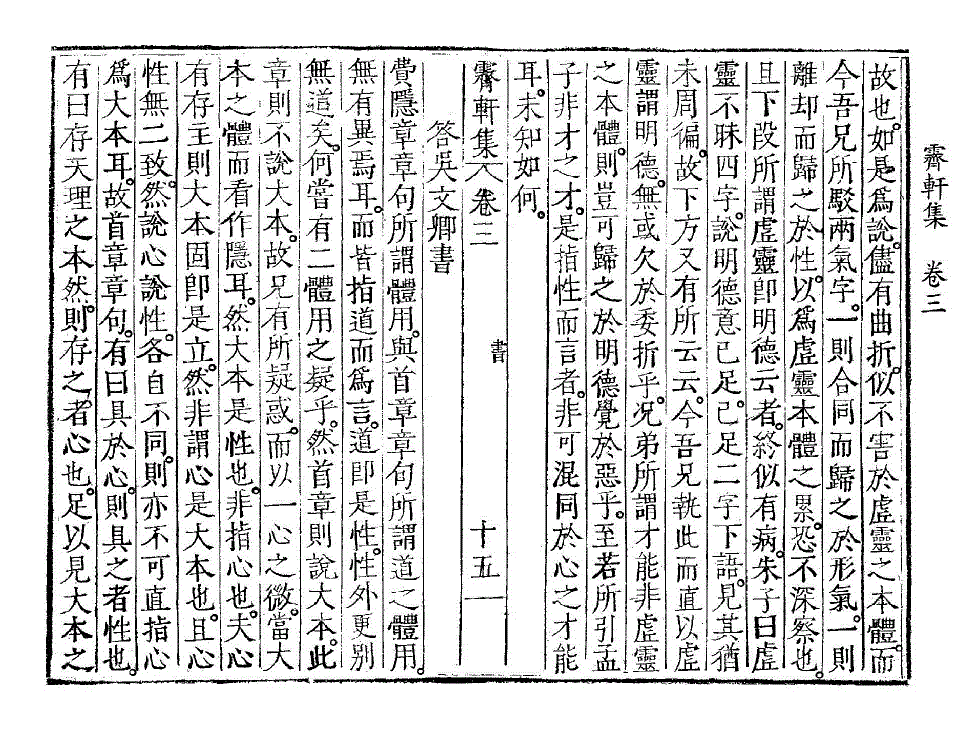 故也。如是为说。尽有曲折。似不害于虚灵之本体。而今吾兄所驳两气字。一则合同而归之于形气。一则离却而归之于性。以为虚灵本体之累。恐不深察也。且下段所谓虚灵即明德云者。终似有病。朱子曰虚灵不昧四字。说明德意已足。已足二字下语。见其犹未周遍。故下方又有所云云。今吾兄执此而直以虚灵谓明德。无或欠于委折乎。况弟所谓才能非虚灵之本体。则岂可归之于明德觉于恶乎。至若所引孟子非才之才。是指性而言者。非可混同于心之才能耳。未知如何。
故也。如是为说。尽有曲折。似不害于虚灵之本体。而今吾兄所驳两气字。一则合同而归之于形气。一则离却而归之于性。以为虚灵本体之累。恐不深察也。且下段所谓虚灵即明德云者。终似有病。朱子曰虚灵不昧四字。说明德意已足。已足二字下语。见其犹未周遍。故下方又有所云云。今吾兄执此而直以虚灵谓明德。无或欠于委折乎。况弟所谓才能非虚灵之本体。则岂可归之于明德觉于恶乎。至若所引孟子非才之才。是指性而言者。非可混同于心之才能耳。未知如何。答吴文卿书
费隐章章句所谓体用。与首章章句所谓道之体用。无有异焉耳。而皆指道而为言。道即是性。性外更别无道矣。何尝有二体用之疑乎。然首章则说大本。此章则不说大本。故兄有所疑惑。而以一心之微。当大本之体而看作隐耳。然大本是性也。非指心也。夫心有存主则大本固即是立。然非谓心是大本也。且心性无二致。然说心说性。各自不同。则亦不可直指心为大本耳。故首章章句。有曰具于心。则具之者性也。有曰存天理之本然。则存之者心也。足以见大本之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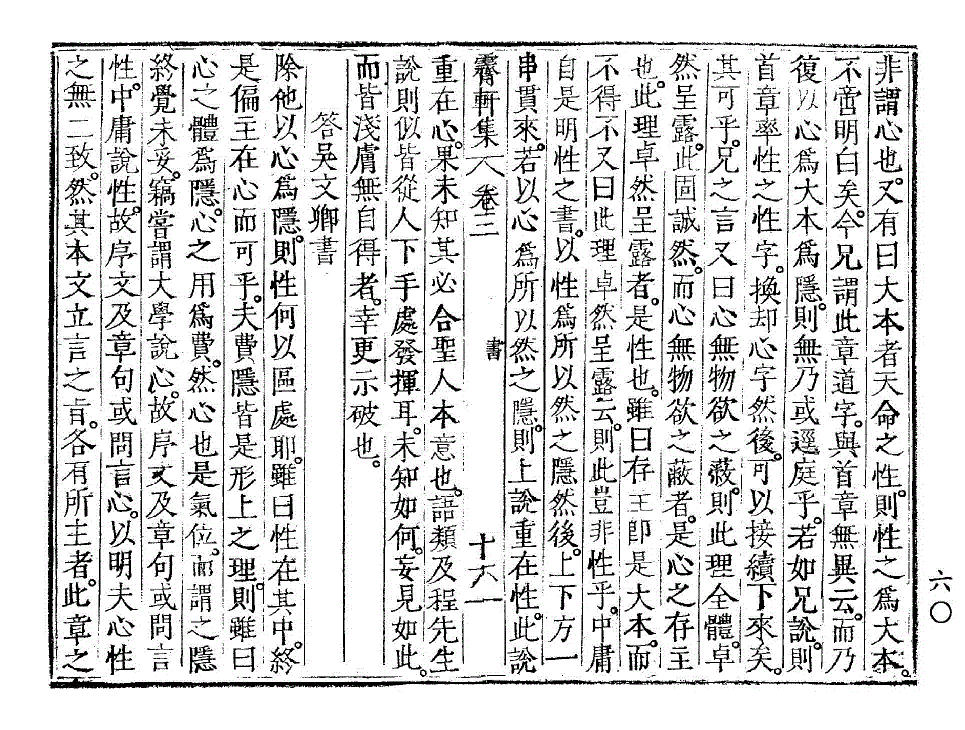 非谓心也。又有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则性之为大本。不啻明白矣。今兄谓此章道字。与首章无异云。而乃复以心为大本为隐。则无乃或径庭乎。若如兄说。则首章率性之性字。换却心字然后。可以接续下来矣。其可乎。兄之言又曰心无物欲之蔽。则此理全体。卓然呈露。此固诚然。而心无物欲之蔽者。是心之存主也。此理卓然呈露者。是性也。虽曰存主即是大本。而不得不又曰此理卓然呈露云。则此岂非性乎。中庸自是明性之书。以性为所以然之隐然后。上下方一串贯来。若以心为所以然之隐。则上说重在性。此说重在心。果未知其必合圣人本意也。语类及程先生说则似皆从人下手处发挥耳。未知如何。妄见如此。而皆浅肤无自得者。幸更示破也。
非谓心也。又有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则性之为大本。不啻明白矣。今兄谓此章道字。与首章无异云。而乃复以心为大本为隐。则无乃或径庭乎。若如兄说。则首章率性之性字。换却心字然后。可以接续下来矣。其可乎。兄之言又曰心无物欲之蔽。则此理全体。卓然呈露。此固诚然。而心无物欲之蔽者。是心之存主也。此理卓然呈露者。是性也。虽曰存主即是大本。而不得不又曰此理卓然呈露云。则此岂非性乎。中庸自是明性之书。以性为所以然之隐然后。上下方一串贯来。若以心为所以然之隐。则上说重在性。此说重在心。果未知其必合圣人本意也。语类及程先生说则似皆从人下手处发挥耳。未知如何。妄见如此。而皆浅肤无自得者。幸更示破也。答吴文卿书
除他以心为隐。则性何以区处耶。虽曰性在其中。终是偏主在心而可乎。夫费隐皆是形上之理。则虽曰心之体为隐。心之用为费。然心也是气位。而谓之隐终觉未妥。窃尝谓大学说心。故序文及章句或问言性。中庸说性。故序文及章句或问言心。以明夫心性之无二致。然其本文立言之旨。各有所主者。此章之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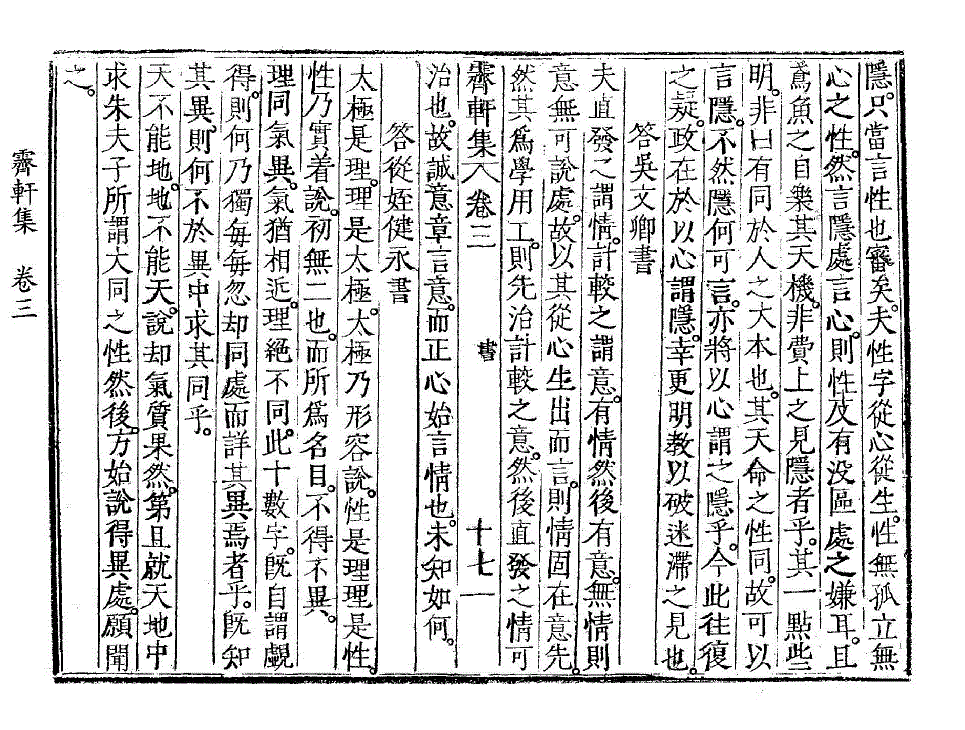 隐。只当言性也审矣。夫性字从心从生。性无孤立无心之性。然言隐处言心。则性反有没区处之嫌耳。且鸢鱼之自乐其天机。非费上之见隐者乎。其一点些明。非曰有同于人之大本也。其天命之性同。故可以言隐。不然隐何可言。亦将以心谓之隐乎。今此往复之疑。政在于以心谓隐。幸更明教以破迷滞之见也。
隐。只当言性也审矣。夫性字从心从生。性无孤立无心之性。然言隐处言心。则性反有没区处之嫌耳。且鸢鱼之自乐其天机。非费上之见隐者乎。其一点些明。非曰有同于人之大本也。其天命之性同。故可以言隐。不然隐何可言。亦将以心谓之隐乎。今此往复之疑。政在于以心谓隐。幸更明教以破迷滞之见也。答吴文卿书
夫直发之谓情。计较之谓意。有情然后有意。无情则意无可说处。故以其从心生出而言。则情固在意先。然其为学用工。则先治计较之意。然后直发之情可治也。故诚意章言意。而正心始言情也。未知如何。
答从侄健永书
太极是理。理是太极。太极乃形容说。性是理理是性。性乃实着说。初无二也。而所为名目。不得不异。
理同气异。气犹相近。理绝不同。此十数字。既自谓觑得。则何乃独每每忽却同处而详其异焉者乎。既知其异。则何不于异中求其同乎。
天不能地。地不能天。说却气质果然。第且就天地中求朱夫子所谓大同之性然后。方始说得异处。愿闻之。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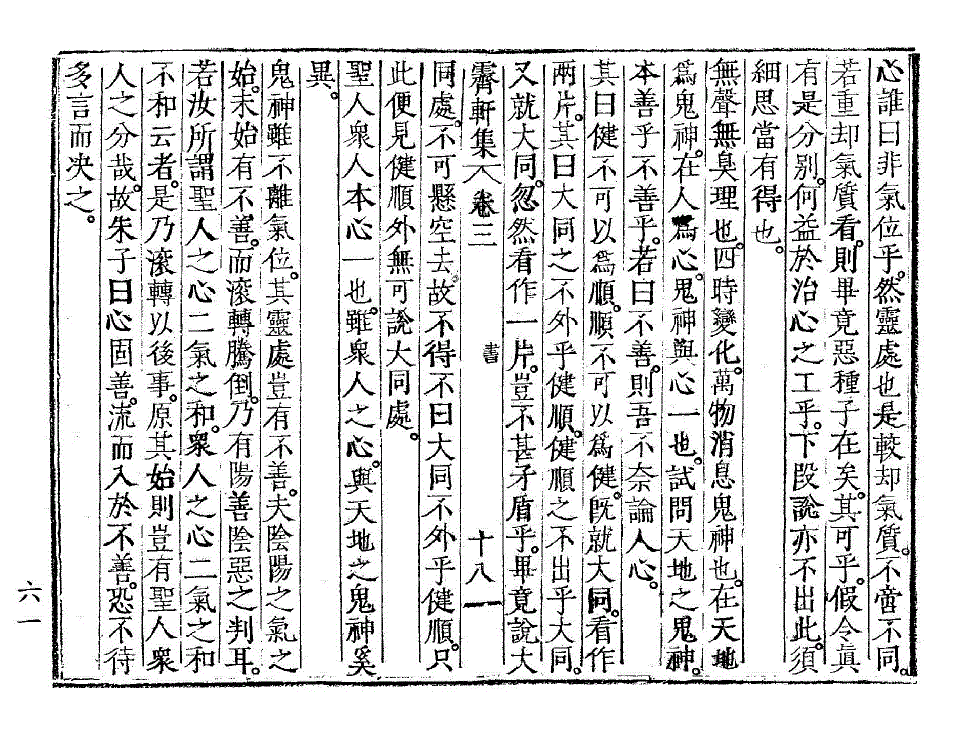 心谁曰非气位乎。然灵处也是较却气质。不啻不同。若重却气质看。则毕竟恶种子在矣。其可乎。假令真有是分别。何益于治心之工乎。下段说亦不出此。须细思当有得也。
心谁曰非气位乎。然灵处也是较却气质。不啻不同。若重却气质看。则毕竟恶种子在矣。其可乎。假令真有是分别。何益于治心之工乎。下段说亦不出此。须细思当有得也。无声无臭理也。四时变化。万物消息鬼神也。在天地为鬼神。在人为心。鬼神与心一也。试问天地之鬼神。本善乎不善乎。若曰不善。则吾不奈论人心。
其曰健不可以为顺。顺不可以为健。既就大同。看作两片。其曰大同之不外乎健顺。健顺之不出乎大同。又就大同。忽然看作一片。岂不甚矛盾乎。毕竟说大同处。不可悬空去。故不得不曰大同不外乎健顺。只此便见健顺外无可说大同处。
圣人众人本心一也。虽众人之心。与天地之鬼神奚异。
鬼神虽不离气位。其灵处岂有不善。夫阴阳之气之始。未始有不善。而滚转腾倒。乃有阳善阴恶之判耳。若汝所谓圣人之心二气之和。众人之心二气之和不和云者。是乃滚转以后事。原其始则岂有圣人众人之分哉。故朱子曰心固善。流而入于不善。恐不待多言而决之。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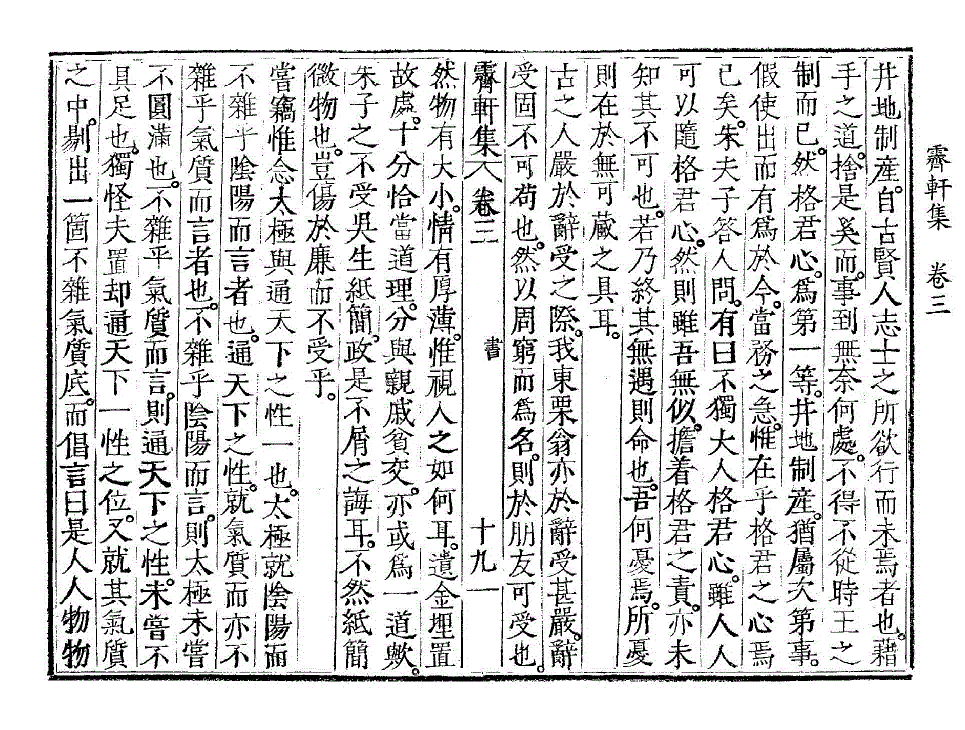 井地制产。自古贤人志士之所欲行而未焉者也。藉手之道。舍是奚而。事到无奈何处。不得不从时王之制而已。然格君心。为第一等。井地制产。犹属次第事。假使出而有为于今。当务之急。惟在乎格君之心焉已矣。朱夫子答人问。有曰不独大人格君心。虽人人可以随格君心。然则虽吾无似。担着格君之责。亦未知其不可也。若乃终其无遇则命也。吾何忧焉。所忧则在于无可藏之具耳。
井地制产。自古贤人志士之所欲行而未焉者也。藉手之道。舍是奚而。事到无奈何处。不得不从时王之制而已。然格君心。为第一等。井地制产。犹属次第事。假使出而有为于今。当务之急。惟在乎格君之心焉已矣。朱夫子答人问。有曰不独大人格君心。虽人人可以随格君心。然则虽吾无似。担着格君之责。亦未知其不可也。若乃终其无遇则命也。吾何忧焉。所忧则在于无可藏之具耳。古之人严于辞受之际。我东栗翁亦于辞受甚严。辞受固不可苟也。然以周穷而为名。则于朋友可受也。然物有大小。情有厚薄。惟视人之如何耳。遗金埋置故处。十分恰当道理。分与亲戚贫交。亦或为一道欤。朱子之不受吴生纸简。政是不屑之诲耳。不然纸简微物也。岂伤于廉而不受乎。
尝窃惟念太极与通天下之性一也。太极就阴阳而不杂乎阴阳而言者也。通天下之性。就气质而亦不杂乎气质而言者也。不杂乎阴阳而言。则太极未尝不圆满也。不杂乎气质而言。则通天下之性。未尝不具足也。独怪夫置却通天下一性之位。又就其气质之中。剔出一个不杂气质底。而倡言曰是人人物物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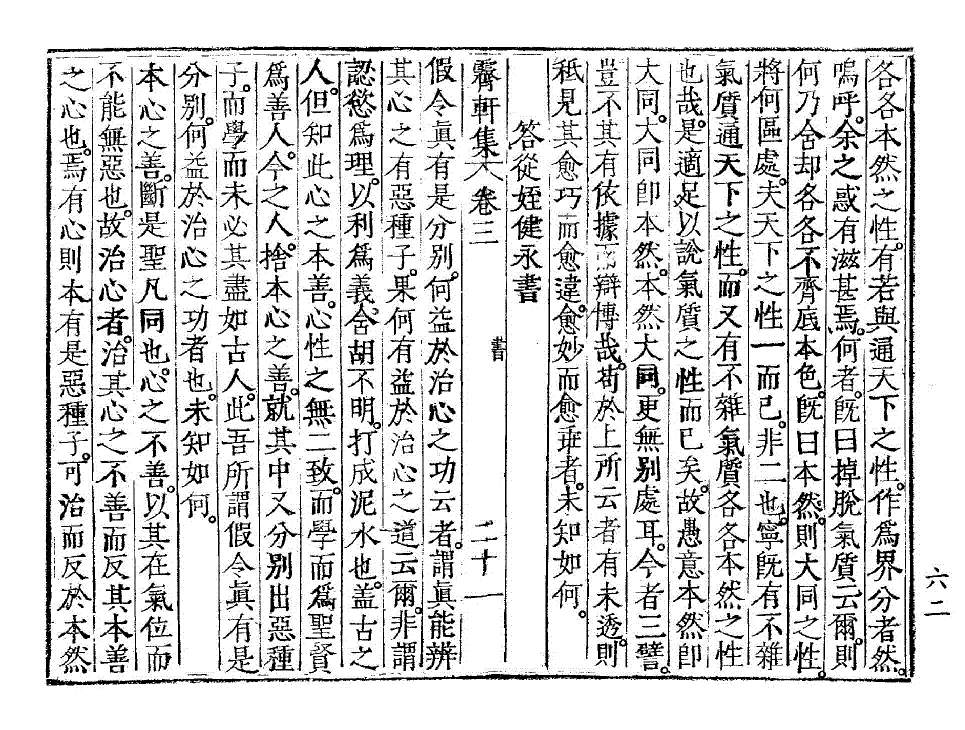 各各本然之性。有若与通天下之性。作为界分者然。呜呼。余之惑有滋甚焉。何者。既曰掉脱气质云尔。则何乃舍却各各不齐底本色。既曰本然。则大同之性。将何区处。夫天下之性一而已。非二也。宁既有不杂气质通天下之性。而又有不杂气质各各本然之性也哉。是适足以说气质之性而已矣。故愚意本然即大同。大同即本然。本然大同。更无别处耳。今者三譬。岂不其有依据而辩博哉。苟于上所云者有未透。则秪见其愈巧而愈违。愈妙而愈乖者。未知如何。
各各本然之性。有若与通天下之性。作为界分者然。呜呼。余之惑有滋甚焉。何者。既曰掉脱气质云尔。则何乃舍却各各不齐底本色。既曰本然。则大同之性。将何区处。夫天下之性一而已。非二也。宁既有不杂气质通天下之性。而又有不杂气质各各本然之性也哉。是适足以说气质之性而已矣。故愚意本然即大同。大同即本然。本然大同。更无别处耳。今者三譬。岂不其有依据而辩博哉。苟于上所云者有未透。则秪见其愈巧而愈违。愈妙而愈乖者。未知如何。答从侄健永书
假令真有是分别。何益于治心之功云者。谓真能辨其心之有恶种子。果何有益于治心之道云尔。非谓认欲为理。以利为义。含胡不明。打成泥水也。盖古之人。但知此心之本善。心性之无二致。而学而为圣贤为善人。今之人。舍本心之善。就其中又分别出恶种子。而学而未必其尽如古人。此吾所谓假令真有是分别。何益于治心之功者也。未知如何。
本心之善。断是圣凡同也。心之不善。以其在气位而不能无恶也。故治心者。治其心之不善而反其本善之心也。焉有心则本有是恶种子。可治而反于本然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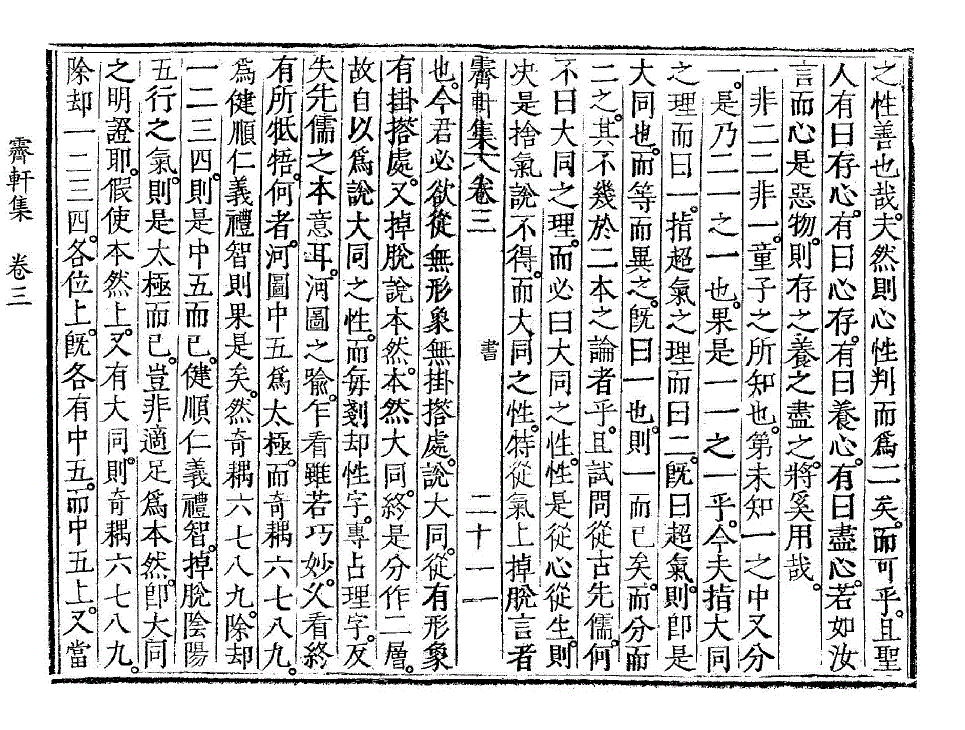 之性善也哉。夫然则心性判而为二矣。而可乎。且圣人有曰存心。有曰心存。有曰养心。有曰尽心。若如汝言而心是恶物。则存之养之尽之。将奚用哉。
之性善也哉。夫然则心性判而为二矣。而可乎。且圣人有曰存心。有曰心存。有曰养心。有曰尽心。若如汝言而心是恶物。则存之养之尽之。将奚用哉。一非二二非一。童子之所知也。第未知一之中又分一。是乃二一之一也。果是一一之一乎。今夫指大同之理而曰一。指超气之理而曰二。既曰超气。则即是大同也。而等而异之。既曰一也。则一而已矣。而分而二之。其不几于二本之论者乎。且试问从古先儒。何不曰大同之理。而必曰大同之性。性是从心从生。则决是舍气说不得。而大同之性。特从气上掉脱言者也。今君必欲从无形象无挂搭处。说大同。从有形象有挂搭处。又掉脱说本然。本然大同。终是分作二层。故自以为说大同之性。而每刬却性字。专占理字。反失先儒之本意耳。河图之喻。乍看虽若巧妙。久看终有所牴牾。何者。河图中五为太极。而奇耦六七八九。为健顺仁义礼智则果是矣。然奇耦六七八九。除却一二三四。则是中五而已。健顺仁义礼智。掉脱阴阳五行之气。则是太极而已。岂非适足为本然。即大同之明證耶。假使本然上。又有大同。则奇耦六七八九。除却一二三四。各位上。既各有中五。而中五上。又当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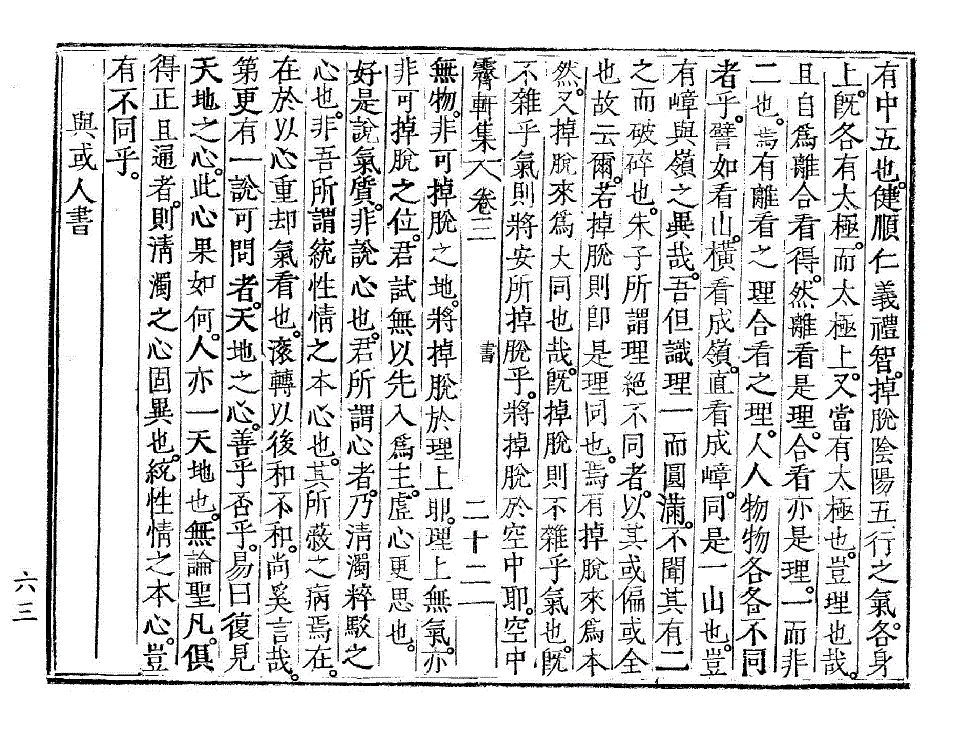 有中五也。健顺仁义礼智。掉脱阴阳五行之气。各身上。既各有太极。而太极上。又当有太极也。岂理也哉。且自为离合看得。然离看是理。合看亦是理。一而非二也。焉有离看之理合看之理。人人物物各各不同者乎。譬如看山。横看成岭。直看成嶂。同是一山也。岂有嶂与岭之异哉。吾但识理一而圆满。不闻其有二之而破碎也。朱子所谓理绝不同者。以其或偏或全也故云尔。若掉脱则即是理同也。焉有掉脱来为本然。又掉脱来为大同也哉。既掉脱则不杂乎气也。既不杂乎气则将安所掉脱乎。将掉脱于空中耶。空中无物。非可掉脱之地。将掉脱于理上耶。理上无气。亦非可掉脱之位。君试无以先入为主。虚心更思也。
有中五也。健顺仁义礼智。掉脱阴阳五行之气。各身上。既各有太极。而太极上。又当有太极也。岂理也哉。且自为离合看得。然离看是理。合看亦是理。一而非二也。焉有离看之理合看之理。人人物物各各不同者乎。譬如看山。横看成岭。直看成嶂。同是一山也。岂有嶂与岭之异哉。吾但识理一而圆满。不闻其有二之而破碎也。朱子所谓理绝不同者。以其或偏或全也故云尔。若掉脱则即是理同也。焉有掉脱来为本然。又掉脱来为大同也哉。既掉脱则不杂乎气也。既不杂乎气则将安所掉脱乎。将掉脱于空中耶。空中无物。非可掉脱之地。将掉脱于理上耶。理上无气。亦非可掉脱之位。君试无以先入为主。虚心更思也。好是说气质。非说心也。君所谓心者。乃清浊粹驳之心也。非吾所谓统性情之本心也。其所蔽之病焉在。在于以心重却气看也。滚转以后和不和。尚奚言哉。第更有一说可问者。天地之心。善乎否乎。易曰复见天地之心。此心果如何。人亦一天地也。无论圣凡。俱得正且通者。则清浊之心固异也。统性情之本心。岂有不同乎。
与或人书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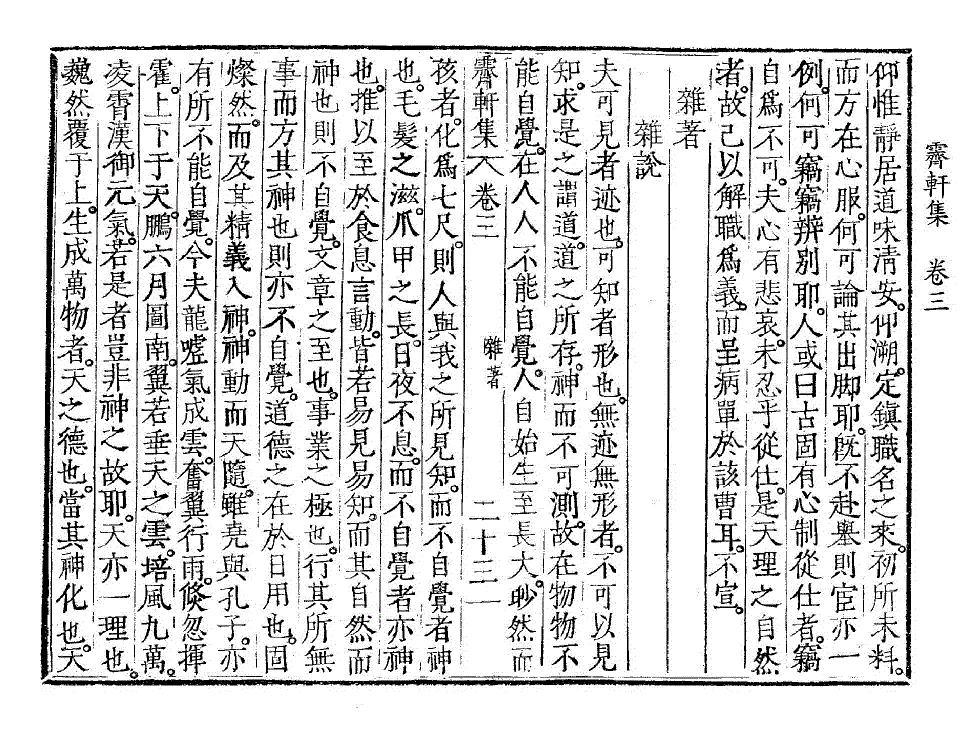 仰惟静居道味清安。仰溯。定镇职名之来。初所未料。而方在心服。何可论其出脚耶。既不赴举则宦亦一例。何可窃窃辨别耶。人或曰古固有心制从仕者。窃自为不可。夫心有悲哀。未忍乎从仕。是天理之自然者。故已以解职为义。而呈病单于该曹耳。不宣。
仰惟静居道味清安。仰溯。定镇职名之来。初所未料。而方在心服。何可论其出脚耶。既不赴举则宦亦一例。何可窃窃辨别耶。人或曰古固有心制从仕者。窃自为不可。夫心有悲哀。未忍乎从仕。是天理之自然者。故已以解职为义。而呈病单于该曹耳。不宣。霁轩集卷之三
杂著
杂说
夫可见者迹也。可知者形也。无迹无形者。不可以见知。求是之谓道。道之所存。神而不可测。故在物物不能自觉。在人人不能自觉。人自始生至长大。眇然而孩者。化为七尺。则人与我之所见知。而不自觉者神也。毛发之滋。爪甲之长。日夜不息。而不自觉者亦神也。推以至于食息言动。皆若易见易知。而其自然而神也则不自觉。文章之至也。事业之极也。行其所无事而方其神也则亦不自觉。道德之在于日用也。固灿然。而及其精义入神。神动而天随。虽尧与孔子。亦有所不能自觉。今夫龙嘘气成云。奋翼行雨。倏忽挥霍。上下于天。鹏六月图南。翼若垂天之云。培风九万。凌霄汉御元气。若是者岂非神之故耶。天亦一理也。巍然覆于上。生成万物者。天之德也。当其神化也。天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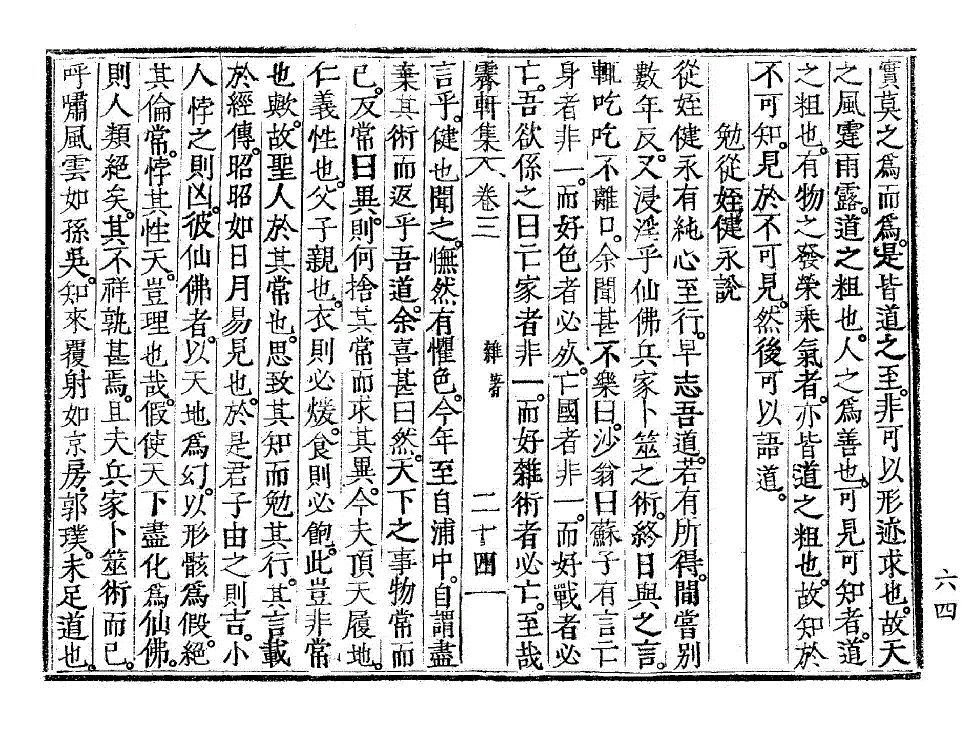 实莫之为而为。是皆道之至。非可以形迹求也。故天之风霆雨露。道之粗也。人之为善也。可见可知者。道之粗也。有物之发荣乘气者。亦皆道之粗也。故知于不可知。见于不可见。然后可以语道。
实莫之为而为。是皆道之至。非可以形迹求也。故天之风霆雨露。道之粗也。人之为善也。可见可知者。道之粗也。有物之发荣乘气者。亦皆道之粗也。故知于不可知。见于不可见。然后可以语道。勉从侄健永说
从侄健永有纯心至行。早志吾道。若有所得。间尝别数年反。又浸淫乎仙佛兵家卜筮之术。终日与之言。辄吃吃不离口。余闻甚不乐曰。沙翁曰苏子有言亡身者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亡国者非一。而好战者必亡。吾欲系之曰亡家者非一。而好杂术者必亡。至哉言乎。健也闻之。怃然有惧色。今年至自浦中。自谓尽弃其术而返乎吾道。余喜甚曰然。天下之事物常而已。反常曰异。则何舍其常而求其异。今夫顶天履地。仁义性也。父子亲也。衣则必煖。食则必饱。此岂非常也欤。故圣人于其常也。思致其知而勉其行。其言载于经传。昭昭如日月易见也。于是君子由之则吉。小人悖之则凶。彼仙佛者。以天地为幻。以形骸为假。绝其伦常。悖其性天。岂理也哉。假使天下尽化为仙佛。则人类绝矣。其不祥孰甚焉。且夫兵家卜筮术而已。呼啸风云如孙吴。知来覆射如京房,郭璞。未足道也。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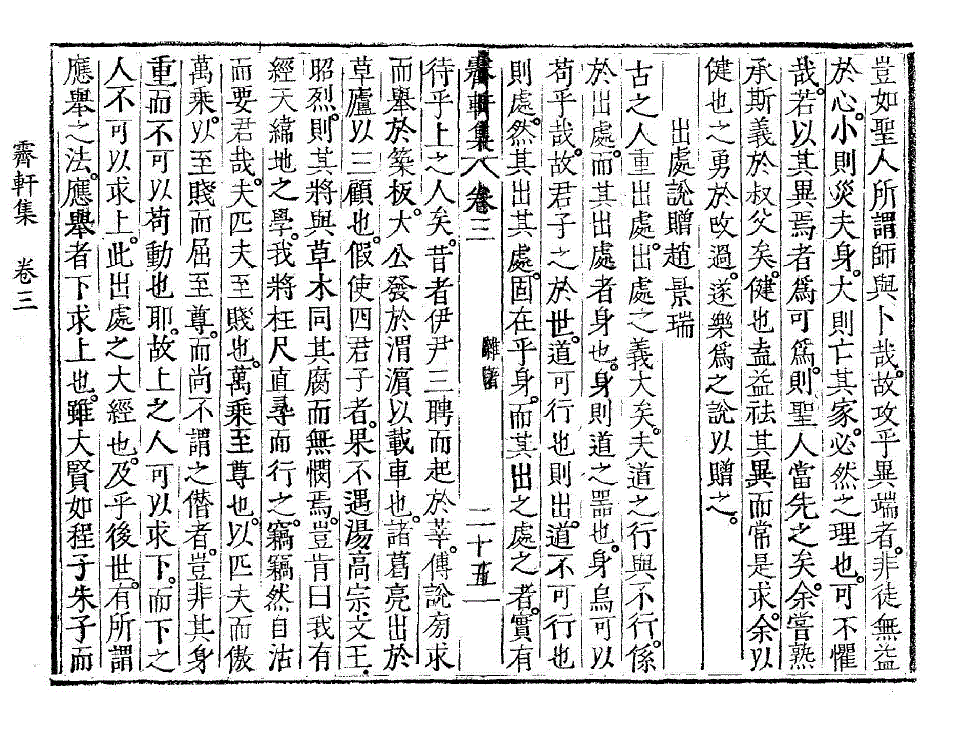 岂如圣人所谓师与卜哉。故攻乎异端者。非徒无益于心。小则灾夫身。大则亡其家。必然之理也。可不惧哉。若以其异焉者为可为。则圣人当先之矣。余尝熟承斯义于叔父矣。健也盍益祛其异而常是求。余以健也之勇于改过。遂乐为之说以赠之。
岂如圣人所谓师与卜哉。故攻乎异端者。非徒无益于心。小则灾夫身。大则亡其家。必然之理也。可不惧哉。若以其异焉者为可为。则圣人当先之矣。余尝熟承斯义于叔父矣。健也盍益祛其异而常是求。余以健也之勇于改过。遂乐为之说以赠之。出处说赠赵景瑞
古之人重出处。出处之义大矣。夫道之行与不行。系于出处。而其出处者身也。身则道之器也。身乌可以苟乎哉。故君子之于世。道可行也则出。道不可行也则处。然其出其处。固在乎身。而其出之处之者。实有待乎上之人矣。昔者伊尹三聘而起于莘。傅说旁求而举于筑板。太公发于渭滨以载车也。诸葛亮出于草庐以三顾也。假使四君子者。果不遇汤,高宗,文王,昭烈。则其将与草木同其腐而无悯焉。岂肯曰我有经天纬地之学。我将枉尺直寻而行之。窃窃然自沽而要君哉。夫匹夫至贱也。万乘至尊也。以匹夫而傲万乘。以至贱而屈至尊。而尚不谓之僭者。岂非其身重而不可以苟动也耶。故上之人可以求下。而下之人不可以求上。此出处之大经也。及乎后世。有所谓应举之法。应举者下求上也。虽大贤如程子朱子而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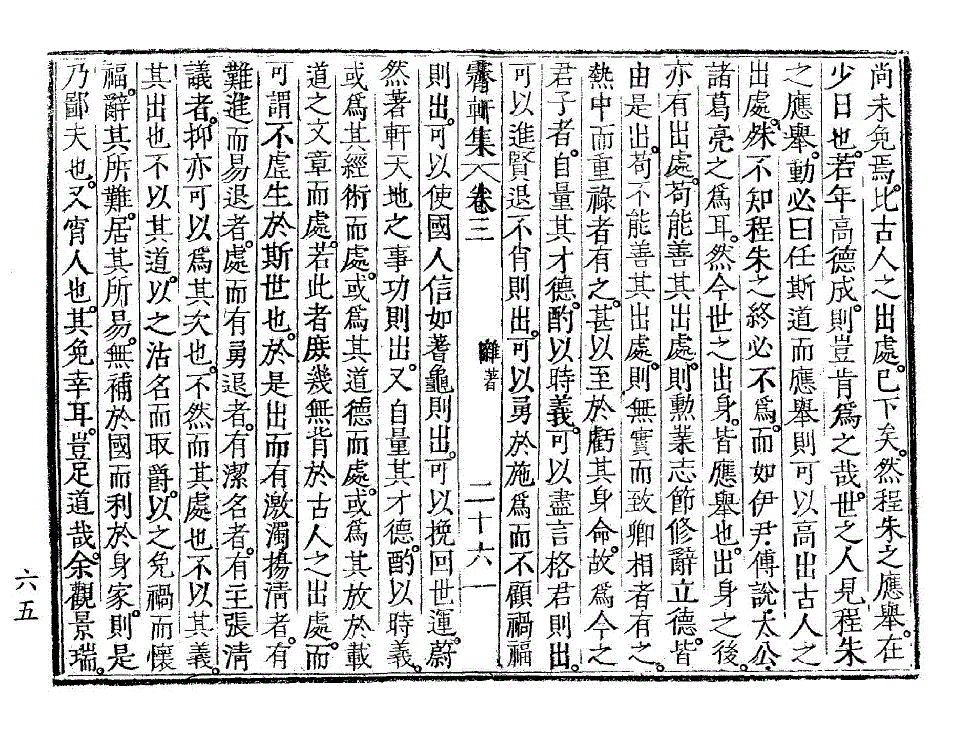 尚未免焉。比古人之出处。已下矣。然程朱之应举。在少日也。若年高德成。则岂肯为之哉。世之人见程朱之应举。动必曰任斯道而应举则可以高出古人之出处。殊不知程朱之终必不为。而如伊尹,傅说,太公,诸葛亮之为耳。然今世之出身。皆应举也。出身之后。亦有出处。苟能善其出处。则勋业志节修辞立德。皆由是出。苟不能善其出处。则无实而致卿相者有之。热中而重禄者有之。甚以至于亏其身命。故为今之君子者。自量其才德。酌以时义。可以尽言格君则出。可以进贤退不肖则出。可以勇于施为而不顾祸福则出。可以使国人信如蓍龟则出。可以挽回世运。蔚然著轩天地之事功则出。又自量其才德。酌以时义。或为其经术而处。或为其道德而处。或为其放于载道之文章而处。若此者庶几无背于古人之出处。而可谓不虚生于斯世也。于是出而有激浊扬清者。有难进而易退者。处而有勇退者。有洁名者。有主张清议者。抑亦可以为其次也。不然而其处也不以其义。其出也不以其道。以之沽名而取爵。以之免祸而怀福。辞其所难。居其所易。无补于国而利于身家。则是乃鄙夫也。又宵人也。其免幸耳。岂足道哉。余观景瑞。
尚未免焉。比古人之出处。已下矣。然程朱之应举。在少日也。若年高德成。则岂肯为之哉。世之人见程朱之应举。动必曰任斯道而应举则可以高出古人之出处。殊不知程朱之终必不为。而如伊尹,傅说,太公,诸葛亮之为耳。然今世之出身。皆应举也。出身之后。亦有出处。苟能善其出处。则勋业志节修辞立德。皆由是出。苟不能善其出处。则无实而致卿相者有之。热中而重禄者有之。甚以至于亏其身命。故为今之君子者。自量其才德。酌以时义。可以尽言格君则出。可以进贤退不肖则出。可以勇于施为而不顾祸福则出。可以使国人信如蓍龟则出。可以挽回世运。蔚然著轩天地之事功则出。又自量其才德。酌以时义。或为其经术而处。或为其道德而处。或为其放于载道之文章而处。若此者庶几无背于古人之出处。而可谓不虚生于斯世也。于是出而有激浊扬清者。有难进而易退者。处而有勇退者。有洁名者。有主张清议者。抑亦可以为其次也。不然而其处也不以其义。其出也不以其道。以之沽名而取爵。以之免祸而怀福。辞其所难。居其所易。无补于国而利于身家。则是乃鄙夫也。又宵人也。其免幸耳。岂足道哉。余观景瑞。霁轩集卷之三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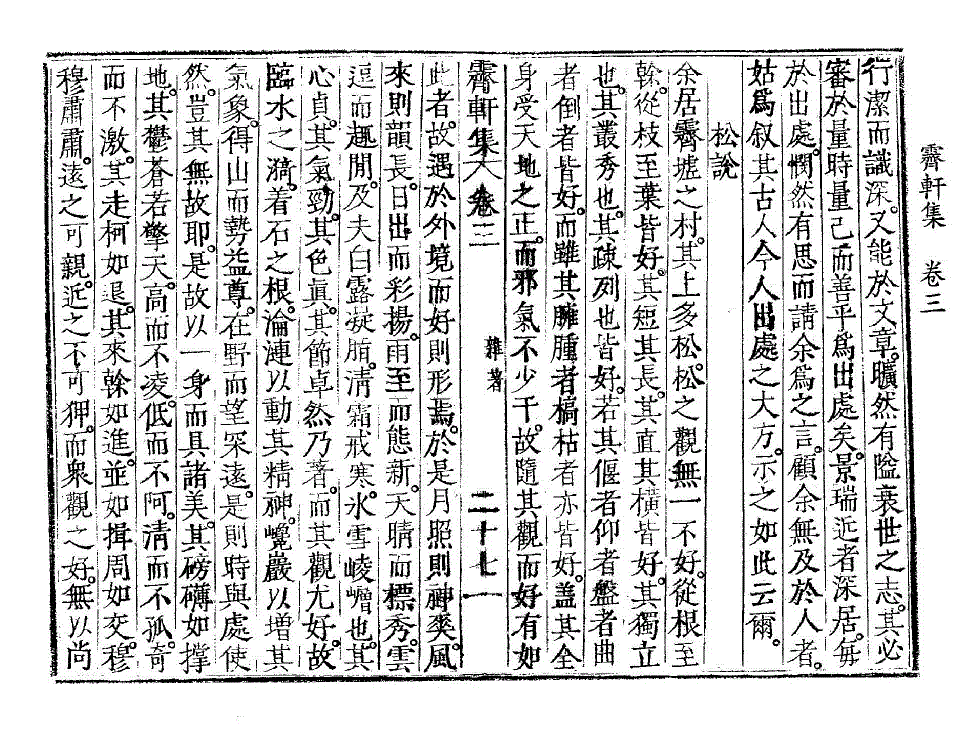 行洁而识深。又能于文章。旷然有隘衰世之志。其必审于量时量己而善乎为出处矣。景瑞近者深居。每于出处。悯然有思而请余为之言。顾余无及于人者。姑为叙其古人今人出处之大方。示之如此云尔。
行洁而识深。又能于文章。旷然有隘衰世之志。其必审于量时量己而善乎为出处矣。景瑞近者深居。每于出处。悯然有思而请余为之言。顾余无及于人者。姑为叙其古人今人出处之大方。示之如此云尔。松说
余居霁墟之村。其上多松。松之观无一不好。从根至干。从枝至叶皆好。其短其长。其直其横皆好。其独立也。其丛秀也。其疏列也皆好。若其偃者仰者盘者曲者倒者皆好。而虽其臃肿者槁枯者亦皆好。盖其全身受天地之正。而邪气不少干。故随其观而好有如此者。故遇于外境而好则形焉。于是月照则神爽。风来则韵长。日出而彩扬。雨至而态新。天晴而标秀。云逗而趣閒。及夫白露凝脂。清霜戒寒。冰雪崚嶒也。其心贞。其气劲。其色真。其节卓然乃著。而其观尤好。故临水之漪。着石之根。沦涟以动其精神。巉岩以增其气象。得山而势益尊。在野而望深远。是则时与处使然。岂其无故耶。是故以一身而具诸美。其磅礴如撑地。其郁苍若擎天。高而不凌。低而不阿。清而不孤。奇而不激。其走柯如退。其来干如进。并如揖周如交。穆穆肃肃。远之可亲。近之不可狎。而众观之好。无以尚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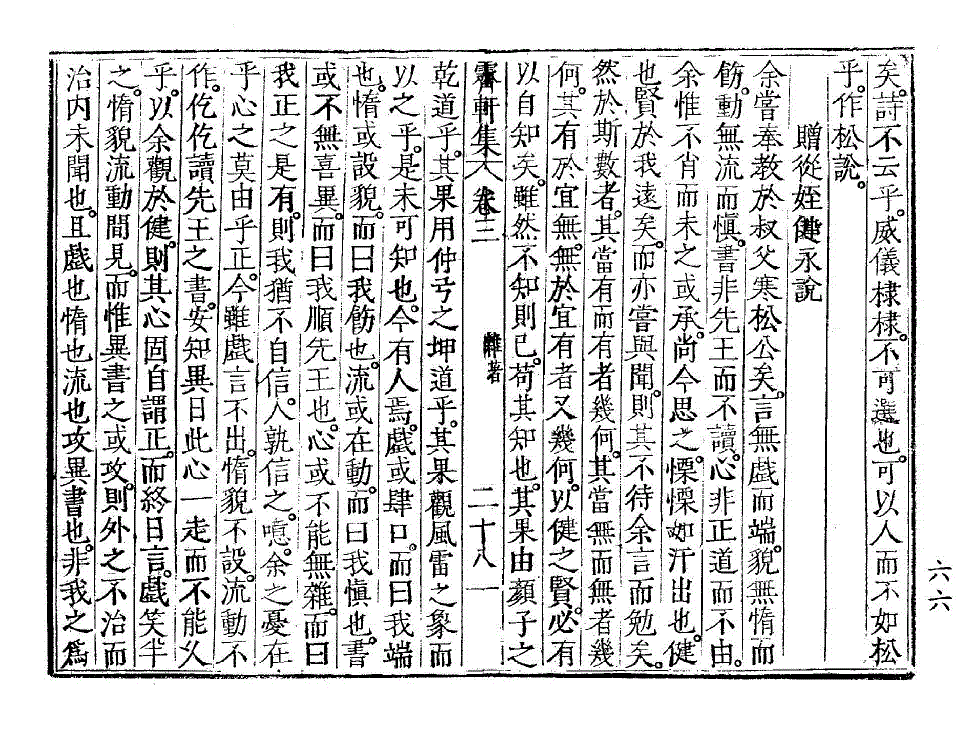 矣。诗不云乎。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可以人而不如松乎。作松说。
矣。诗不云乎。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可以人而不如松乎。作松说。赠从侄健永说
余尝奉教于叔父寒松公矣。言无戏而端。貌无惰而饬。动无流而慎。书非先王而不读。心非正道而不由。余惟不肖而未之或承。尚今思之。慄慄如汗出也。健也贤于我远矣。而亦尝与闻。则其不待余言而勉矣。然于斯数者。其当有而有者几何。其当无而无者几何。其有于宜无。无于宜有者又几何。以健之贤。必有以自知矣。虽然不知则已。苟其知也。其果由颜子之乾道乎。其果用仲弓之坤道乎。其果观风雷之象而以之乎。是未可知也。今有人焉。戏或肆口。而曰我端也。惰或设貌。而曰我饬也。流或在动。而曰我慎也。书或不无喜异。而曰我顺先王也。心或不能无杂。而曰我正之是有。则我犹不自信。人孰信之。噫。余之忧在乎心之莫由乎正。今虽戏言不出。惰貌不设。流动不作。仡仡读先王之书。安知异日此心一走而不能久乎。以余观于健。则其心固自谓正。而终日言。戏笑半之。惰貌流动间见。而惟异书之或攻。则外之不治而治内未闻也。且戏也惰也流也攻异书也。非我之为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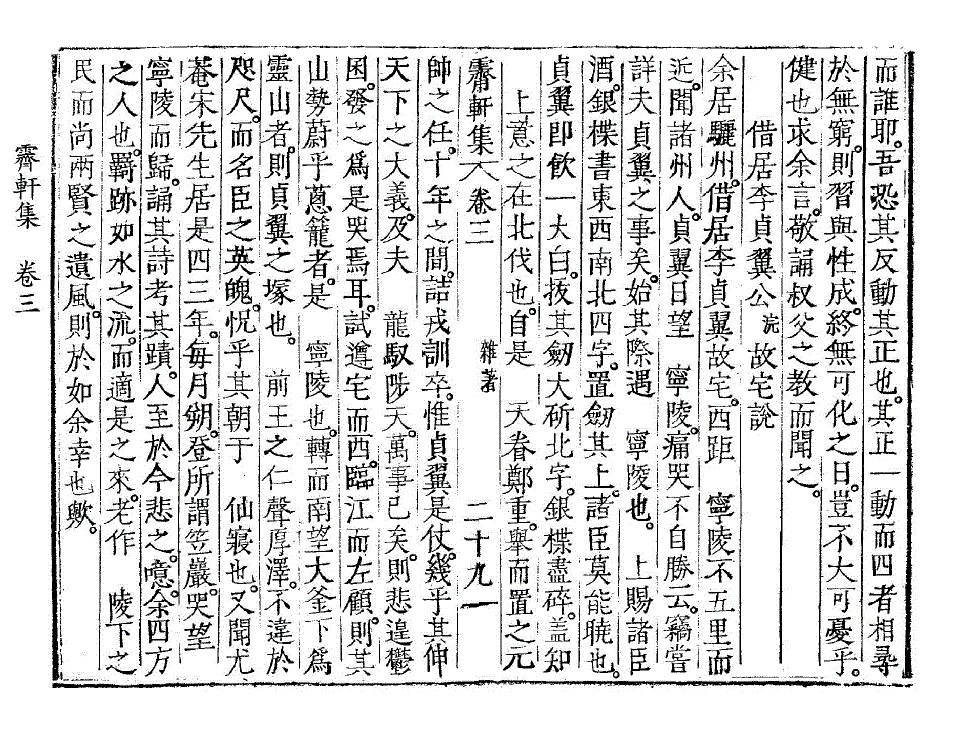 而谁耶。吾恐其反动其正也。其正一动而四者相寻于无穷。则习与性成。终无可化之日。岂不大可忧乎。健也求余言。敬诵叔父之教而闻之。
而谁耶。吾恐其反动其正也。其正一动而四者相寻于无穷。则习与性成。终无可化之日。岂不大可忧乎。健也求余言。敬诵叔父之教而闻之。借居李贞翼公(浣)故宅说
余居骊州。借居李贞翼故宅。西距 宁陵不五里而近。闻诸州人。贞翼日望 宁陵。痛哭不自胜云。窃尝详夫贞翼之事矣。始其际遇 宁陵也。 上赐诸臣酒。银楪书东西南北四字。置剑其上。诸臣莫能晓也。贞翼即饮一大白。拔其剑大斫北字。银楪尽碎。盖知 上意之在北伐也。自是 天眷郑重。举而置之元帅之任。十年之间。诘戎训卒。惟贞翼是仗。几乎其伸天下之大义。及夫 龙驭陟天。万事已矣。则悲遑郁囷。发之为是哭焉耳。试遵宅而西。临江而左顾。则其山势蔚乎葱笼者。是 宁陵也。转而南望大釜下为灵山者。则贞翼之冢也。 前王之仁声厚泽。不违于咫尺。而名臣之英魄。恍乎其朝于 仙寝也。又闻尤庵宋先生居是四三年。每月朔。登所谓笠岩。哭望 宁陵而归。诵其诗考其迹。人至于今悲之。噫。余四方之人也。羁迹如水之流。而适是之来。老作 陵下之民而尚两贤之遗风。则于如余幸也欤。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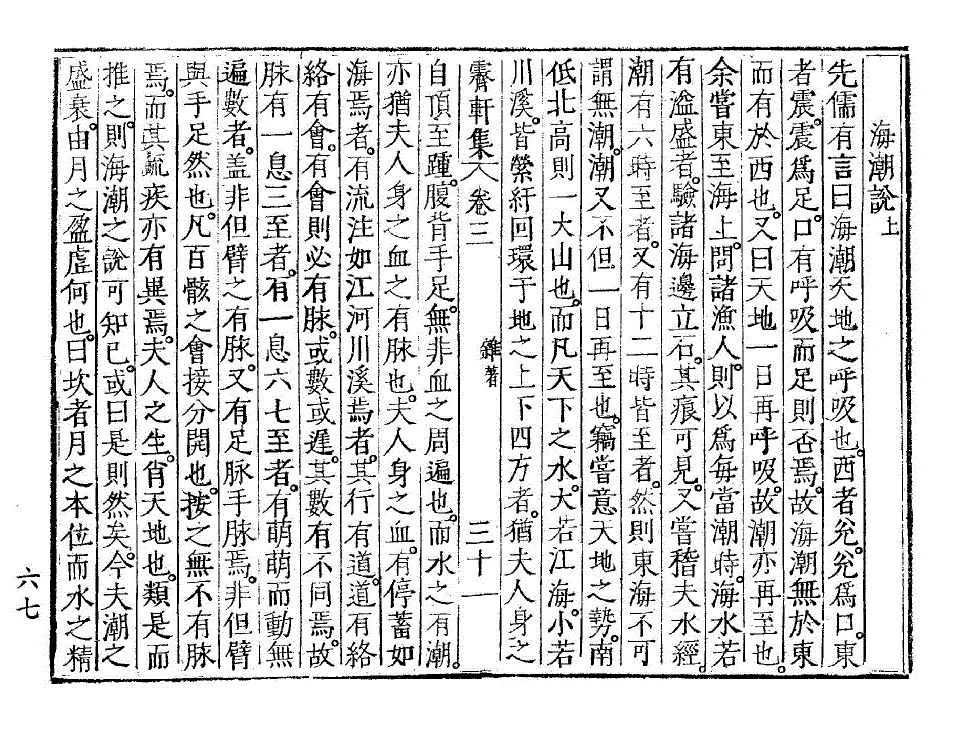 海潮说[上]
海潮说[上]先儒有言曰海潮天地之呼吸也。西者兑。兑为口。东者震。震为足。口有呼吸而足则否焉。故海潮无于东而有于西也。又曰天地一日再呼吸。故潮亦再至也。余尝东至海上。问诸渔人。则以为每当潮时。海水若有溢盛者。验诸海边立石。其痕可见。又尝稽夫水经。潮有六时至者。又有十二时皆至者。然则东海不可谓无潮。潮又不但一日再至也。窃尝意天地之势。南低北高则一大山也。而凡天下之水。大若江海。小若川溪。皆萦纡回环于地之上下四方者。犹夫人身之自顶至踵。腹背手足。无非血之周遍也。而水之有潮。亦犹夫人身之血之有脉也。夫人身之血。有停蓄如海焉者。有流注如江河川溪焉者。其行有道。道有络络有会。有会则必有脉。或数或迟。其数有不同焉。故脉有一息三至者。有一息六七至者。有萌萌而动无遍数者。盖非但臂之有脉。又有足脉手脉焉。非但臂与手足然也。凡百骸之会接分开也。按之无不有脉焉。而其疏疾亦有异焉。夫人之生。肖天地也。类是而推之。则海潮之说可知已。或曰是则然矣。今夫潮之盛衰。由月之盈虚何也。曰坎者月之本位而水之精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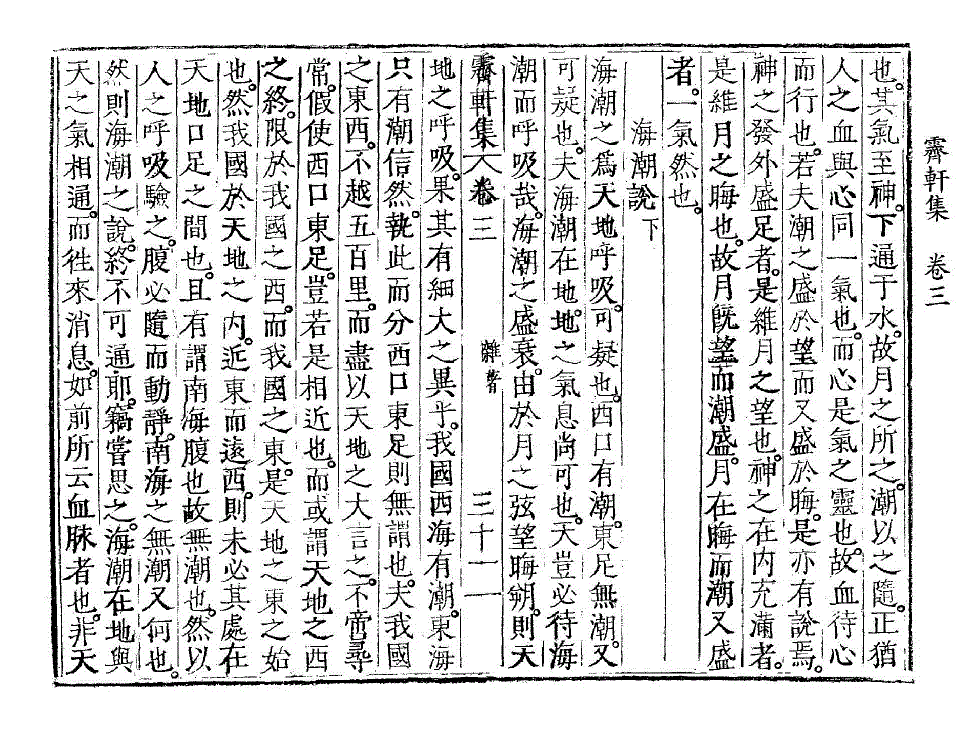 也。其气至神。下通于水。故月之所之。潮以之随。正犹人之血与心同一气也。而心是气之灵也。故血待心而行也。若夫潮之盛于望而又盛于晦。是亦有说焉。神之发外盛足者。是维月之望也。神之在内充满者。是维月之晦也。故月既望而潮盛。月在晦而潮又盛者。一气然也。
也。其气至神。下通于水。故月之所之。潮以之随。正犹人之血与心同一气也。而心是气之灵也。故血待心而行也。若夫潮之盛于望而又盛于晦。是亦有说焉。神之发外盛足者。是维月之望也。神之在内充满者。是维月之晦也。故月既望而潮盛。月在晦而潮又盛者。一气然也。海潮说[下]
海潮之为天地呼吸。可疑也。西口有潮。东足无潮。又可疑也。夫海潮在地。地之气息尚可也。天岂必待海潮而呼吸哉。海潮之盛衰。由于月之弦望晦朔。则天地之呼吸。果其有细大之异乎。我国西海有潮。东海只有潮信然。执此而分西口东足则无谓也。夫我国之东西。不越五百里。而尽以天地之大言之。不啻寻常。假使西口东足。岂若是相近也。而或谓天地之西之终。限于我国之西。而我国之东。是天地之东之始也。然我国于天地之内。近东而远西。则未必其处在天地口足之间也。且有谓南海腹也故无潮也。然以人之呼吸验之。腹必随而动静。南海之无潮又何也。然则海潮之说。终不可通耶。窃尝思之。海潮在地与天之气相通。而往来消息。如前所云血脉者也。非天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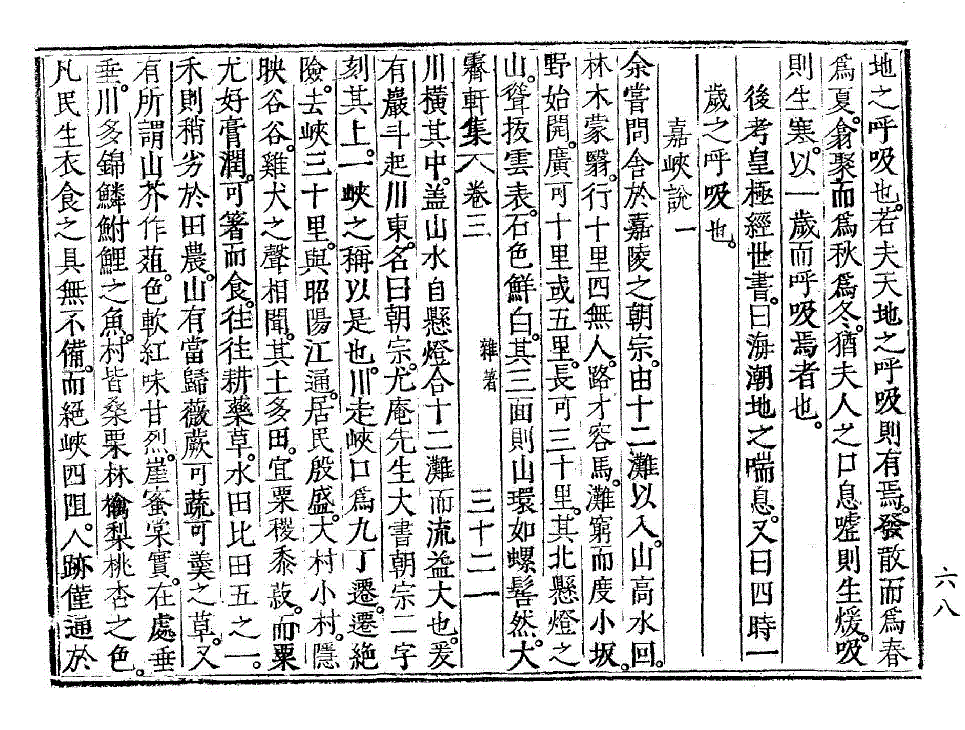 地之呼吸也。若夫天地之呼吸则有焉。发散而为春为夏。翕聚而为秋为冬。犹夫人之口息嘘则生煖。吸则生寒。以一岁而呼吸焉者也。
地之呼吸也。若夫天地之呼吸则有焉。发散而为春为夏。翕聚而为秋为冬。犹夫人之口息嘘则生煖。吸则生寒。以一岁而呼吸焉者也。后考皇极经世书。曰海潮地之喘息。又曰四时一岁之呼吸也。
嘉峡说[一]
余尝问舍于嘉陵之朝宗。由十二滩以入。山高水回。林木蒙翳。行十里四无人。路才容马。滩穷而度小坂。野始开。广可十里或五里。长可三十里。其北悬灯之山。耸拔云表。石色鲜白。其三面则山环如螺髻然。大川横其中。盖山水自悬灯合十二滩而流益大也。爰有岩斗起川东。名曰朝宗。尤庵先生大书朝宗二字刻其上。一峡之称以是也。川走峡口为九丁迁。迁绝险。去峡三十里。与昭阳江通。居民殷盛。大村小村。隐映谷谷。鸡犬之声相闻。其土多田。宜粟稷黍菽。而粟尤好膏润。可箸而食。往往耕药草。水田比田五之一。禾则稍劣于田农。山有当归薇蕨可蔬可羹之草。又有所谓山芥作菹。色软红味甘烈。崖蜜棠实。在处垂垂。川多锦鳞鲋鲤之鱼。村皆桑栗林檎梨桃杏之色。凡民生衣食之具无不备。而绝峡四阻。人迹仅通于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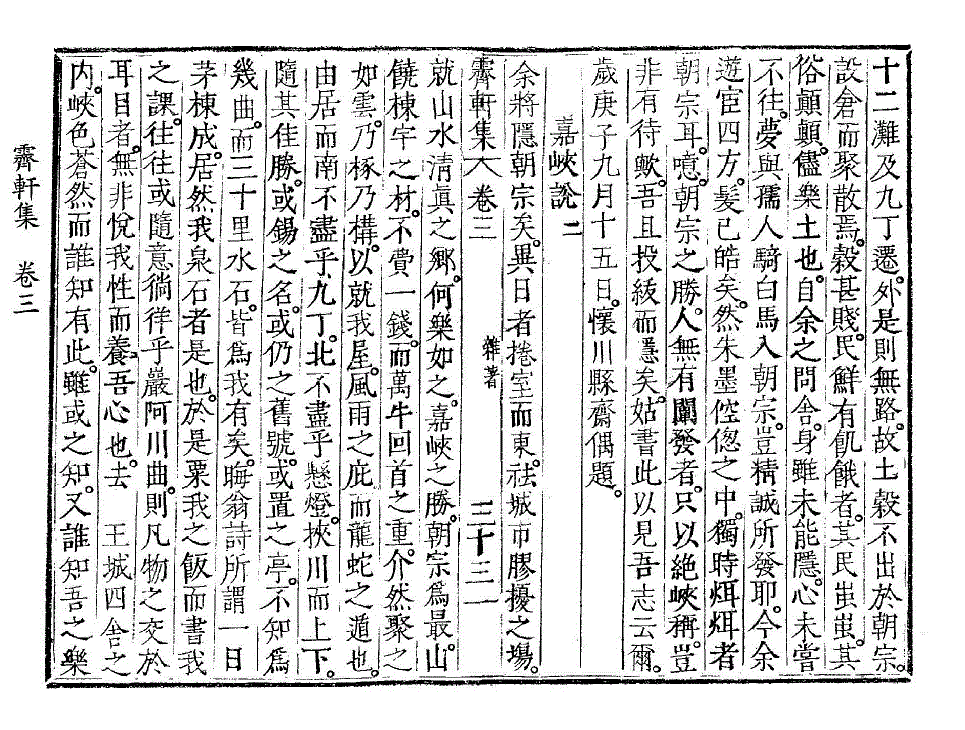 十二滩及九丁迁。外是则无路。故土谷不出于朝宗。设仓而聚散焉。谷甚贱。民鲜有饥饿者。其民蚩蚩。其俗颠颠。尽乐土也。自余之问舍。身虽未能隐。心未尝不往。梦与孺人骑白马入朝宗。岂精诚所发耶。今余游宦四方。发已皓矣。然朱墨倥偬之中。独时耿耿者朝宗耳。噫。朝宗之胜。人无有阐发者。只以绝峡称。岂非有待欤。吾且投绂而隐矣。姑书此以见吾志云尔。岁庚子九月十五日。怀川县斋偶题。
十二滩及九丁迁。外是则无路。故土谷不出于朝宗。设仓而聚散焉。谷甚贱。民鲜有饥饿者。其民蚩蚩。其俗颠颠。尽乐土也。自余之问舍。身虽未能隐。心未尝不往。梦与孺人骑白马入朝宗。岂精诚所发耶。今余游宦四方。发已皓矣。然朱墨倥偬之中。独时耿耿者朝宗耳。噫。朝宗之胜。人无有阐发者。只以绝峡称。岂非有待欤。吾且投绂而隐矣。姑书此以见吾志云尔。岁庚子九月十五日。怀川县斋偶题。嘉峡说[二]
余将隐朝宗矣。异日者捲室而东。祛城韨胶扰之场。就山水清真之乡。何乐如之。嘉峡之胜。朝宗为最。山饶栋宇之材。不费一钱。而万牛回首之重。介然聚之如云。乃椓乃构。以就我屋。风雨之庇而龙蛇之遁也。由居而南不尽乎九丁。北不尽乎悬灯。挟川而上下。随其佳胜。或锡之名。或仍之旧号。或置之亭。不知为几曲。而三十里水石。皆为我有矣。晦翁诗所谓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者是也。于是粟我之饭而书我之课。往往或随意徜徉乎岩阿川曲。则凡物之交于耳目者。无非悦我性而养吾心也。去 王城四舍之内。峡色苍然而谁知有此。虽或之知。又谁知吾之乐
霁轩集卷之三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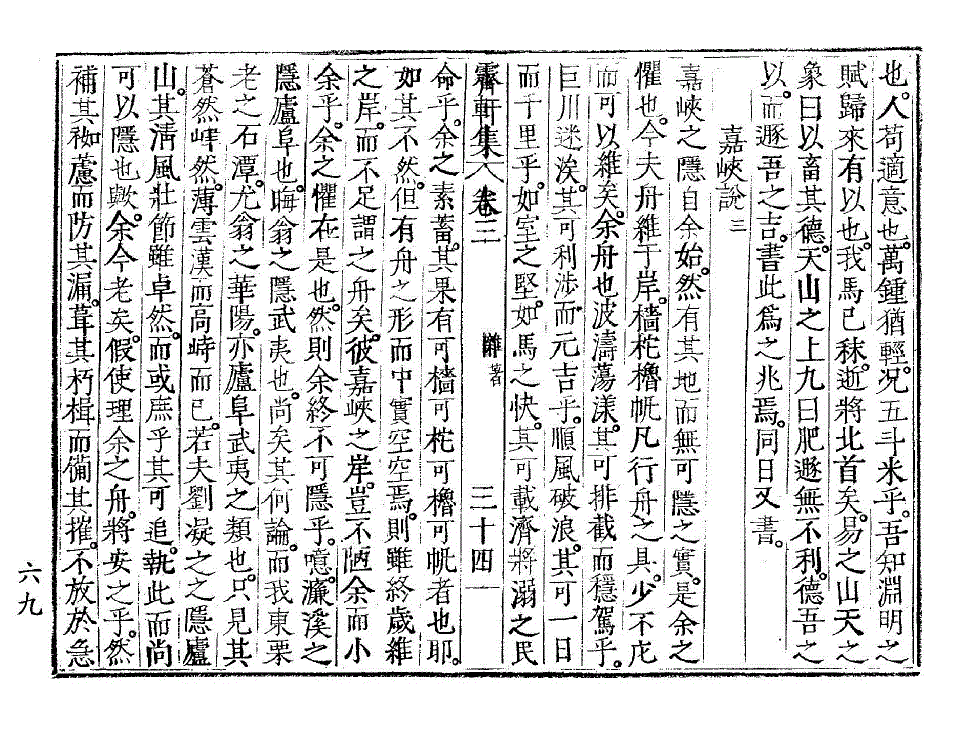 也。人苟适意也。万钟犹轻。况五斗米乎。吾知渊明之赋归来有以也。我马已秣。逝将北首矣。易之山天之象曰以畜其德。天山之上九曰肥遁无不利。德吾之以。而遁吾之吉。书此为之兆焉。同日又书。
也。人苟适意也。万钟犹轻。况五斗米乎。吾知渊明之赋归来有以也。我马已秣。逝将北首矣。易之山天之象曰以畜其德。天山之上九曰肥遁无不利。德吾之以。而遁吾之吉。书此为之兆焉。同日又书。嘉峡说[三]
嘉峡之隐自余始。然有其地而无可隐之实。是余之惧也。今夫舟维于岸。樯柁橹帆凡行舟之具。少不庀而可以维矣。余舟也波涛荡漾。其可排截而稳驾乎。巨川迷涘。其可利涉而元吉乎。顺风破浪。其可一日而千里乎。如室之坚。如马之快。其可载济将溺之民命乎。余之素蓄。其果有可樯可柁可橹可帆者也耶。如其不然。但有舟之形而中实空空焉。则虽终岁维之岸。而不足谓之舟矣。彼嘉峡之岸。岂不陋余而小余乎。余之惧在是也。然则余终不可隐乎。噫。濂溪之隐庐阜也。晦翁之隐武夷也。尚矣其何论。而我东栗老之石潭。尤翁之华阳。亦庐阜武夷之类也。只见其苍然峍然。薄云汉而高峙而已。若夫刘凝之之隐庐山。其清风壮节虽卓然。而或庶乎其可追。执此而尚可以隐也欤。余今老矣。假使理余之舟。将安之乎。然补其袽藘而防其漏。葺其朽楫而备其摧。不放于急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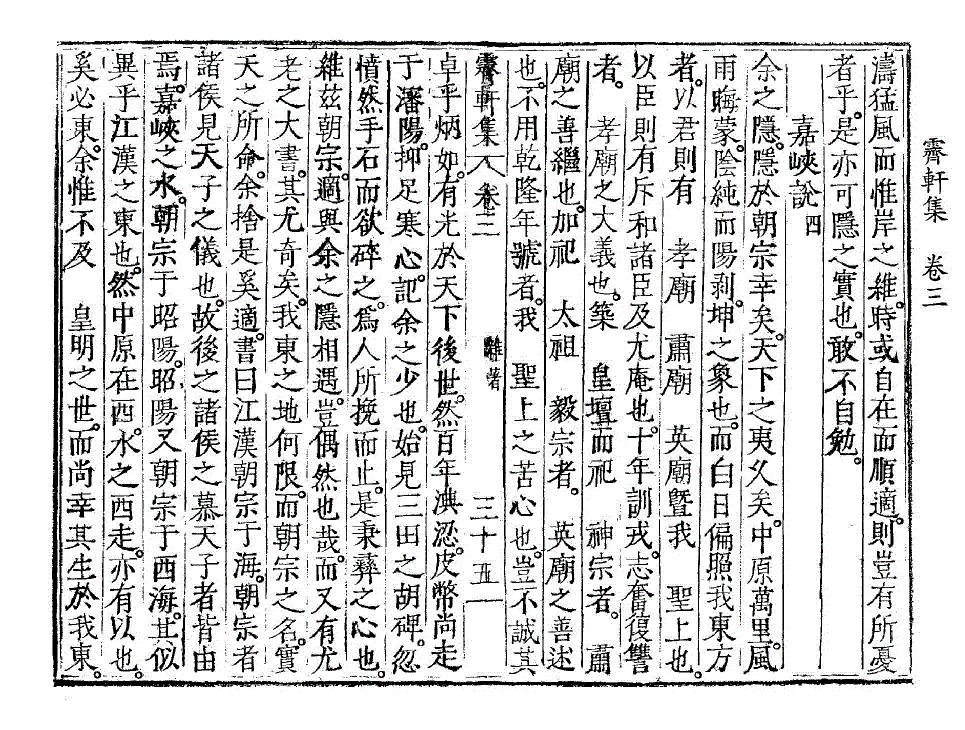 涛猛风而惟岸之维。时或自在而顺适。则岂有所忧者乎。是亦可隐之实也。敢不自勉。
涛猛风而惟岸之维。时或自在而顺适。则岂有所忧者乎。是亦可隐之实也。敢不自勉。嘉峡说[四]
余之隐。隐于朝宗幸矣。天下之夷久矣。中原万里。风雨晦蒙。阴纯而阳剥。坤之象也。而白日偏照我东方者。以君则有 孝庙 肃庙 英庙暨我 圣上也。以臣则有斥和诸臣及尤庵也。十年训戎。志奋复雠者。 孝庙之大义也。筑 皇坛而祀 神宗者。 肃庙之善继也。加祀 太祖 毅宗者。 英庙之善述也。不用乾隆年号者。我 圣上之苦心也。岂不诚其卓乎炳如。有光于天下后世。然百年淟涊。皮币尚走于沈阳。抑足寒心。记余之少也。始见三田之胡碑。忽愤然手石而欲碎之。为人所挽而止。是秉彝之心也。维玆朝宗。适与余之隐相遇。岂偶然也哉。而又有尤老之大书。其尤奇矣。我东之地何限。而朝宗之名。实天之所命。余舍是奚适。书曰江汉朝宗于海。朝宗者诸侯见天子之仪也。故后之诸侯之慕天子者皆由焉。嘉峡之水。朝宗于昭阳。昭阳又朝宗于西海。其似异乎江汉之东也。然中原在西。水之西走。亦有以也。奚必东。余惟不及 皇明之世。而尚幸其生于我东。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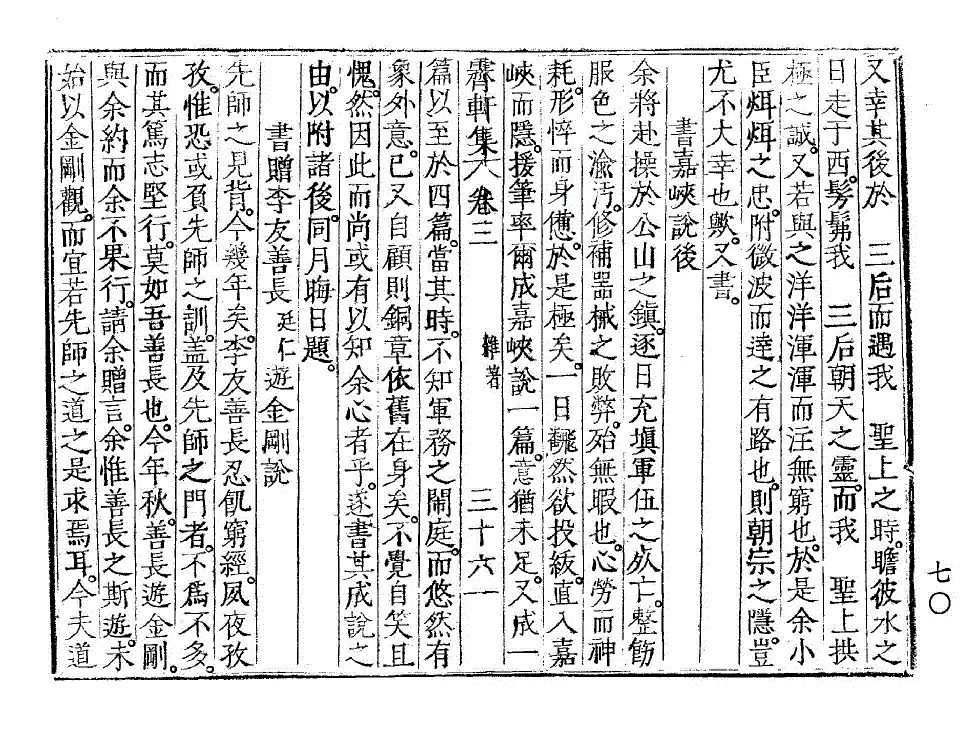 又幸其后于 三后而遇我 圣上之时。瞻彼水之日走于西。髣髴我 三后朝天之灵。而我 圣上拱极之诚。又若与之洋洋浑浑而注无穷也。于是余小臣耿耿之忠。附微波而达之有路也。则朝宗之隐。岂尤不大幸也欤。又书。
又幸其后于 三后而遇我 圣上之时。瞻彼水之日走于西。髣髴我 三后朝天之灵。而我 圣上拱极之诚。又若与之洋洋浑浑而注无穷也。于是余小臣耿耿之忠。附微波而达之有路也。则朝宗之隐。岂尤不大幸也欤。又书。书嘉峡说后
余将赴操于公山之镇。逐日充填军伍之死亡。整饬服色之渝污。修补器械之败弊。殆无暇也。心劳而神耗。形悴而身惫。于是极矣。一日翻然欲投绂。直入嘉峡而隐。援笔率尔成嘉峡说一篇。意犹未足。又成一篇以至于四篇。当其时。不知军务之闹庭。而悠然有象外意。已又自顾则铜章依旧在身矣。不觉自笑且愧。然因此而尚或有以知余心者乎。遂书其成说之由。以附诸后。同月晦日题。
书赠李友善长(廷仁)游金刚说
先师之见背。今几年矣。李友善长忍饥穷经。夙夜孜孜。惟恐或负先师之训。盖及先师之门者。不为不多。而其笃志坚行。莫如吾善长也。今年秋。善长游金刚。与余约而余不果行。请余赠言。余惟善长之斯游。未始以金刚观。而宜若先师之道之是求焉耳。今夫道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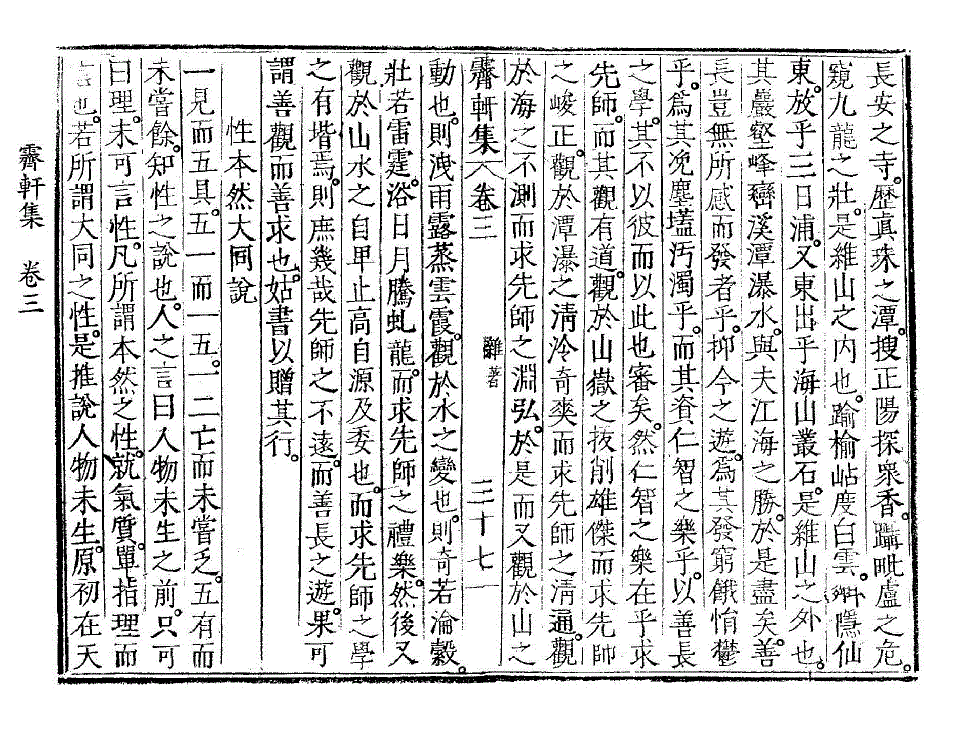 长安之寺。历真珠之潭。搜正阳探众香。蹑毗卢之危。窥九龙之壮。是维山之内也。踰榆岾度白云。𦗲隐仙东。放乎三日浦。又东出乎海山丛石。是维山之外也。其岩壑峰峦溪潭瀑水。与夫江海之胜。于是尽矣。善长岂无所感而发者乎。抑今之游。为其发穷饿悁郁乎。为其浼尘壒污浊乎。而其资仁智之乐乎。以善长之学。其不以彼而以此也审矣。然仁智之乐在乎求先师。而其观有道。观于山岳之拔削雄杰而求先师之峻正。观于潭瀑之清泠奇爽而求先师之清通。观于海之不测而求先师之渊弘。于是而又观于山之动也。则泄雨露蒸云霞。观于水之变也。则奇若沦縠。壮若雷霆。浴日月腾虬龙。而求先师之礼乐。然后又观于山水之自卑止高自源及委也。而求先师之学之有阶焉。则庶几哉先师之不远。而善长之游。果可谓善观而善求也。姑书以赠其行。
长安之寺。历真珠之潭。搜正阳探众香。蹑毗卢之危。窥九龙之壮。是维山之内也。踰榆岾度白云。𦗲隐仙东。放乎三日浦。又东出乎海山丛石。是维山之外也。其岩壑峰峦溪潭瀑水。与夫江海之胜。于是尽矣。善长岂无所感而发者乎。抑今之游。为其发穷饿悁郁乎。为其浼尘壒污浊乎。而其资仁智之乐乎。以善长之学。其不以彼而以此也审矣。然仁智之乐在乎求先师。而其观有道。观于山岳之拔削雄杰而求先师之峻正。观于潭瀑之清泠奇爽而求先师之清通。观于海之不测而求先师之渊弘。于是而又观于山之动也。则泄雨露蒸云霞。观于水之变也。则奇若沦縠。壮若雷霆。浴日月腾虬龙。而求先师之礼乐。然后又观于山水之自卑止高自源及委也。而求先师之学之有阶焉。则庶几哉先师之不远。而善长之游。果可谓善观而善求也。姑书以赠其行。性本然大同说
一见而五具。五一而一五。一二亡而未尝乏。五有而未尝馀。知性之说也。人之言曰人物未生之前。只可曰理。未可言性。凡所谓本然之性。就气质。单指理而言也。若所谓大同之性。是推说人物未生。原初在天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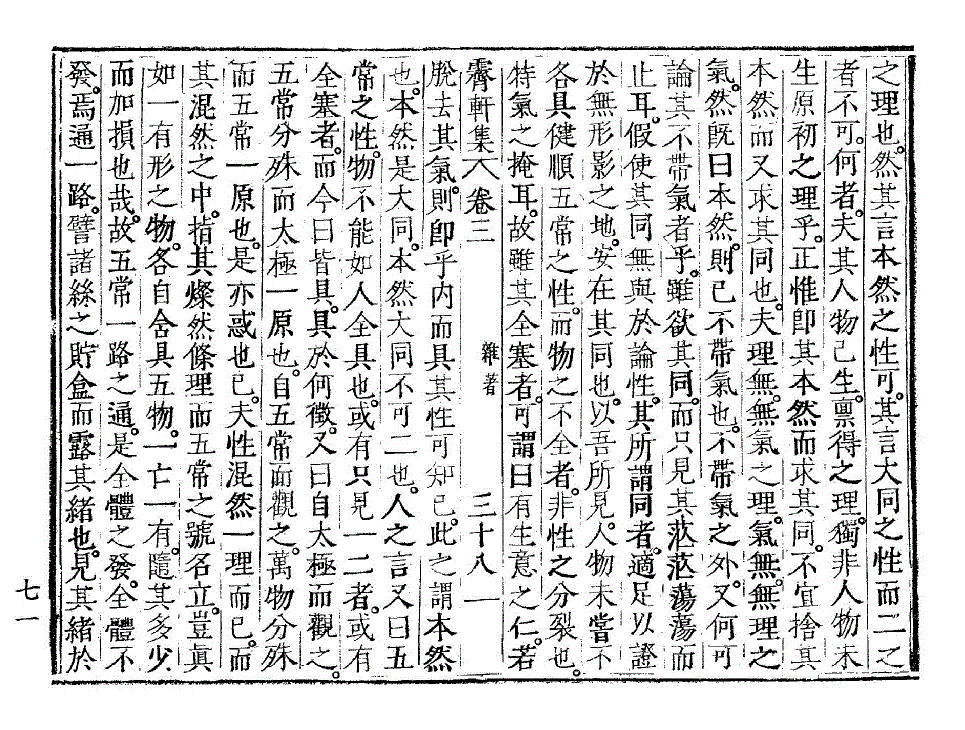 之理也。然其言本然之性可。其言大同之性而二之者不可。何者。夫其人物已生。禀得之理。独非人物未生原初之理乎。正惟即其本然而求其同。不宜舍其本然而又求其同也。夫理无。无气之理。气无。无理之气。然既曰本然。则已不带气也。不带气之外。又何可论其不带气者乎。虽欲其同。而只见其茫茫荡荡而止耳。假使其同无与于论性。其所谓同者。适足以證于无形影之地。安在其同也。以吾所见。人物未尝不各具健顺五常之性。而物之不全者。非性之分裂也。特气之掩耳。故虽其全塞者。可谓曰有生意之仁。若脱去其气。则即乎内而具其性可知已。此之谓本然也。本然是大同。本然大同不可二也。人之言又曰五常之性。物不能如人全具也。或有只见一二者。或有全塞者。而今曰皆具。具于何徵。又曰自太极而观之。五常分殊而太极一原也。自五常而观之。万物分殊而五常一原也。是亦惑也已。夫性混然一理而已。而其混然之中。指其灿然条理而五常之号名立。岂真如一有形之物。各自含具五物。一亡一有。随其多少而加损也哉。故五常一路之通。是全体之发。全体不发。焉通一路。譬诸丝之贮盒而露其绪也。见其绪于
之理也。然其言本然之性可。其言大同之性而二之者不可。何者。夫其人物已生。禀得之理。独非人物未生原初之理乎。正惟即其本然而求其同。不宜舍其本然而又求其同也。夫理无。无气之理。气无。无理之气。然既曰本然。则已不带气也。不带气之外。又何可论其不带气者乎。虽欲其同。而只见其茫茫荡荡而止耳。假使其同无与于论性。其所谓同者。适足以證于无形影之地。安在其同也。以吾所见。人物未尝不各具健顺五常之性。而物之不全者。非性之分裂也。特气之掩耳。故虽其全塞者。可谓曰有生意之仁。若脱去其气。则即乎内而具其性可知已。此之谓本然也。本然是大同。本然大同不可二也。人之言又曰五常之性。物不能如人全具也。或有只见一二者。或有全塞者。而今曰皆具。具于何徵。又曰自太极而观之。五常分殊而太极一原也。自五常而观之。万物分殊而五常一原也。是亦惑也已。夫性混然一理而已。而其混然之中。指其灿然条理而五常之号名立。岂真如一有形之物。各自含具五物。一亡一有。随其多少而加损也哉。故五常一路之通。是全体之发。全体不发。焉通一路。譬诸丝之贮盒而露其绪也。见其绪于霁轩集卷之三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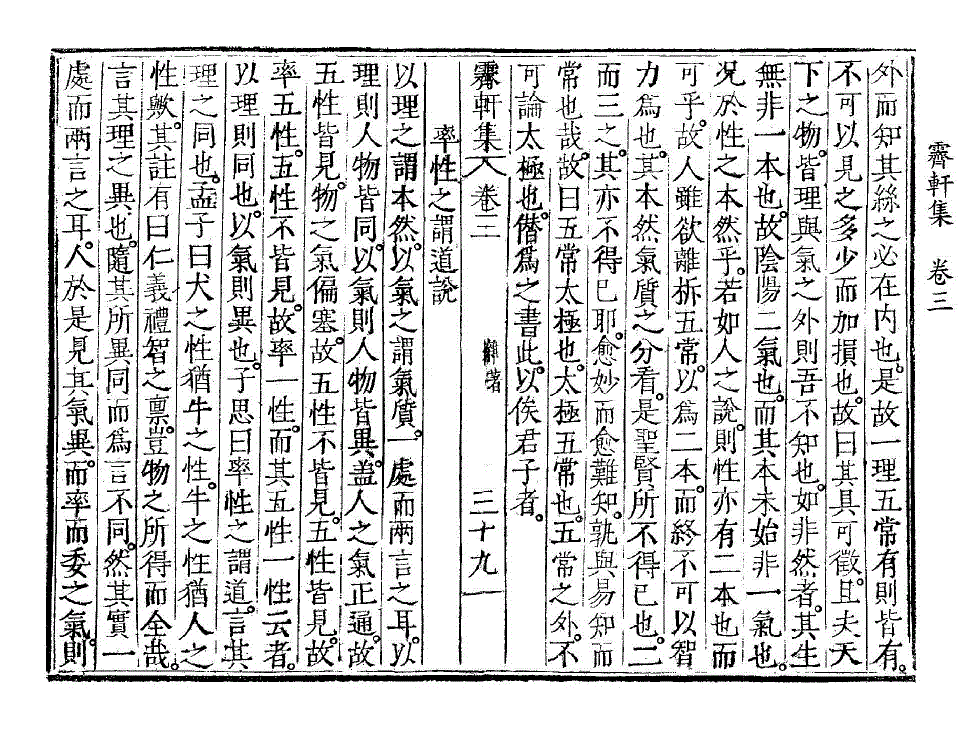 外而知其丝之必在内也。是故一理五常有则皆有。不可以见之多少而加损也。故曰其具可徵。且夫天下之物。皆理与气之外则吾不知也。如非然者。其生无非一本也。故阴阳二气也。而其本未始非一气也。况于性之本然乎。若如人之说。则性亦有二本也而可乎。故人虽欲离析五常。以为二本。而终不可以智力为也。其本然气质之分看。是圣贤所不得已也。二而三之。其亦不得已耶。愈妙而愈难知。孰与易知而常也哉。故曰五常太极也。太极五常也。五常之外。不可论太极也。僭为之书此。以俟君子者。
外而知其丝之必在内也。是故一理五常有则皆有。不可以见之多少而加损也。故曰其具可徵。且夫天下之物。皆理与气之外则吾不知也。如非然者。其生无非一本也。故阴阳二气也。而其本未始非一气也。况于性之本然乎。若如人之说。则性亦有二本也而可乎。故人虽欲离析五常。以为二本。而终不可以智力为也。其本然气质之分看。是圣贤所不得已也。二而三之。其亦不得已耶。愈妙而愈难知。孰与易知而常也哉。故曰五常太极也。太极五常也。五常之外。不可论太极也。僭为之书此。以俟君子者。率性之谓道说
以理之谓本然。以气之谓气质。一处而两言之耳。以理则人物皆同。以气则人物皆异。盖人之气正通。故五性皆见。物之气偏塞。故五性不皆见。五性皆见。故率五性。五性不皆见。故率一性。而其五性一性云者。以理则同也。以气则异也。子思曰率性之谓道。言其理之同也。孟子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其注有曰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言其理之异也。随其所异同而为言不同。然其实一处而两言之耳。人于是见其气异。而率而委之气。则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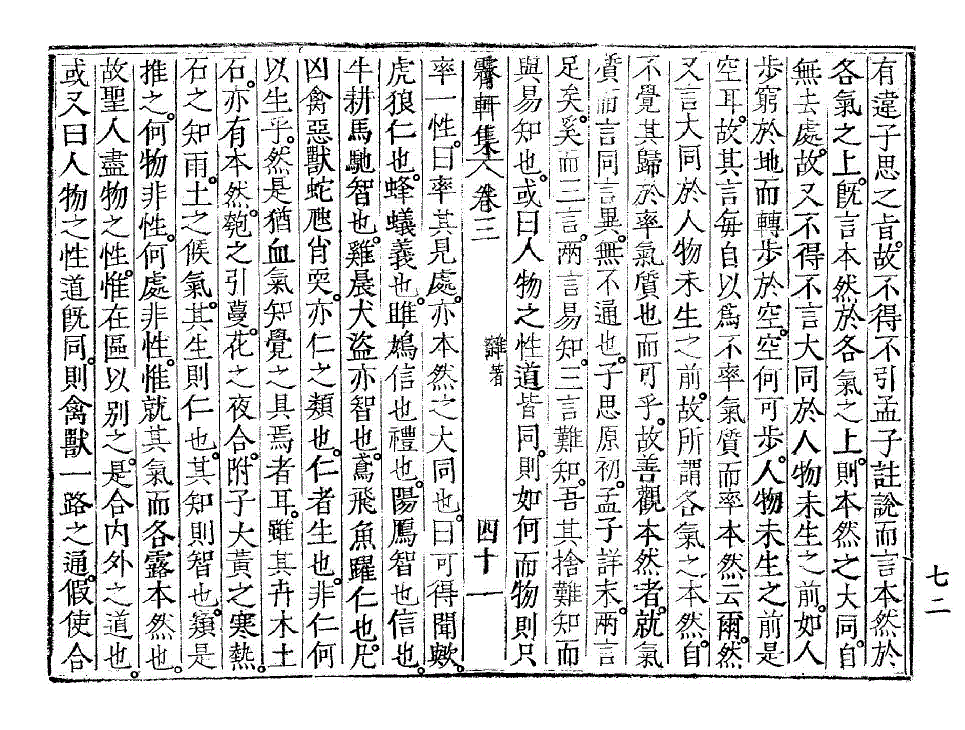 有违子思之旨。故不得不引孟子注说而言本然于各气之上。既言本然于各气之上。则本然之大同。自无去处。故又不得不言大同于人物未生之前。如人步穷于地而转步于空。空何可步。人物未生之前是空耳。故其言每自以为不率气质而率本然云尔。然又言大同于人物未生之前。故所谓各气之本然。自不觉其归于率气质也而可乎。故善观本然者。就气质而言同言异。无不通也。子思原初。孟子详末。两言足矣。奚而三言。两言易知。三言难知。吾其舍难知而与易知也。或曰人物之性道皆同。则如何而物则只率一性。曰率其见处。亦本然之大同也。曰可得闻欤。虎狼仁也。蜂蚁义也。雎鸠信也礼也。阳雁智也信也。牛耕马驰智也。鸡晨犬盗亦智也。鸢飞鱼跃仁也。凡凶禽恶兽蛇虺肖耎。亦仁之类也。仁者生也。非仁何以生乎。然是犹血气知觉之具焉者耳。虽其卉木土石。亦有本然。匏之引蔓。花之夜合。附子大黄之寒热。石之知雨。土之候气。其生则仁也。其知则智也。类是推之。何物非性。何处非性。惟就其气而各露本然也。故圣人尽物之性。惟在区以别之。是合内外之道也。或又曰人物之性道既同。则禽兽一路之通。假使合
有违子思之旨。故不得不引孟子注说而言本然于各气之上。既言本然于各气之上。则本然之大同。自无去处。故又不得不言大同于人物未生之前。如人步穷于地而转步于空。空何可步。人物未生之前是空耳。故其言每自以为不率气质而率本然云尔。然又言大同于人物未生之前。故所谓各气之本然。自不觉其归于率气质也而可乎。故善观本然者。就气质而言同言异。无不通也。子思原初。孟子详末。两言足矣。奚而三言。两言易知。三言难知。吾其舍难知而与易知也。或曰人物之性道皆同。则如何而物则只率一性。曰率其见处。亦本然之大同也。曰可得闻欤。虎狼仁也。蜂蚁义也。雎鸠信也礼也。阳雁智也信也。牛耕马驰智也。鸡晨犬盗亦智也。鸢飞鱼跃仁也。凡凶禽恶兽蛇虺肖耎。亦仁之类也。仁者生也。非仁何以生乎。然是犹血气知觉之具焉者耳。虽其卉木土石。亦有本然。匏之引蔓。花之夜合。附子大黄之寒热。石之知雨。土之候气。其生则仁也。其知则智也。类是推之。何物非性。何处非性。惟就其气而各露本然也。故圣人尽物之性。惟在区以别之。是合内外之道也。或又曰人物之性道既同。则禽兽一路之通。假使合霁轩集卷之三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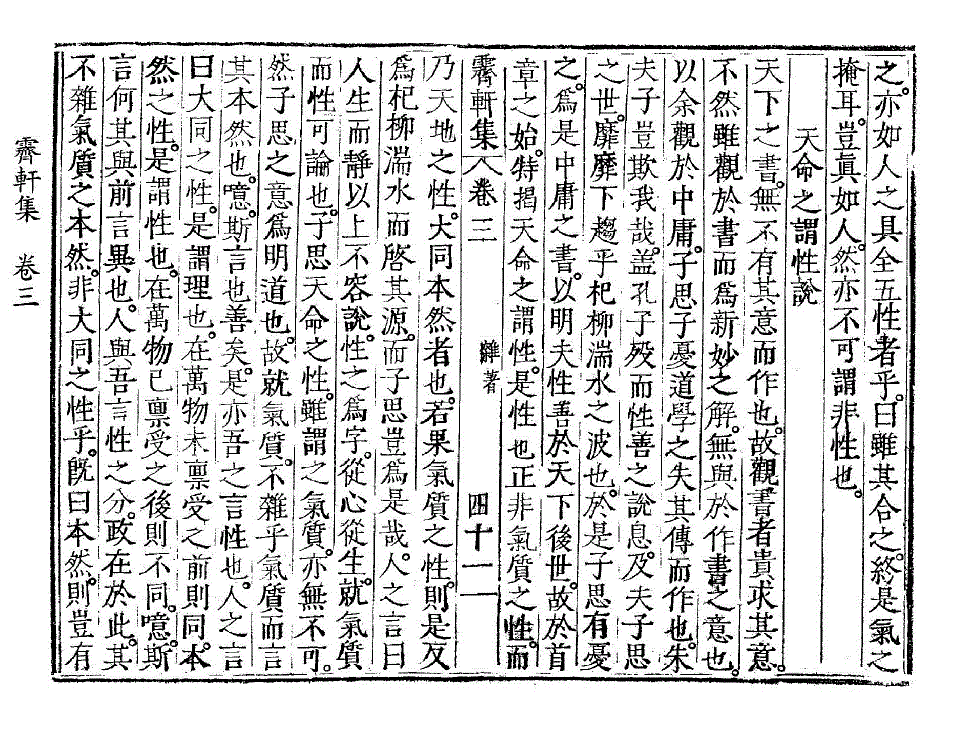 之。亦如人之具全五性者乎。曰虽其合之。终是气之掩耳。岂真如人。然亦不可谓非性也。
之。亦如人之具全五性者乎。曰虽其合之。终是气之掩耳。岂真如人。然亦不可谓非性也。天命之谓性说
天下之书。无不有其意而作也。故观书者贵求其意。不然虽观于书而为新妙之解。无与于作书之意也。以余观于中庸。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夫子岂欺我哉。盖孔子殁而性善之说息。及夫子思之世。靡靡下趋乎杞柳湍水之波也。于是子思有忧之。为是中庸之书。以明夫性善于天下后世。故于首章之始。特揭天命之谓性。是性也正非气质之性。而乃天地之性。大同本然者也。若果气质之性。则是反为杞柳湍水而启其源。而子思岂为是哉。人之言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性之为字。从心从生。就气质而性可论也。子思天命之性。虽谓之气质。亦无不可。然子思之意为明道也。故就气质。不杂乎气质而言其本然也。噫。斯言也善矣。是亦吾之言性也。人之言曰大同之性。是谓理也。在万物未禀受之前则同。本然之性。是谓性也。在万物已禀受之后则不同。噫。斯言何其与前言异也。人与吾言性之分。政在于此。其不杂气质之本然。非大同之性乎。既曰本然。则岂有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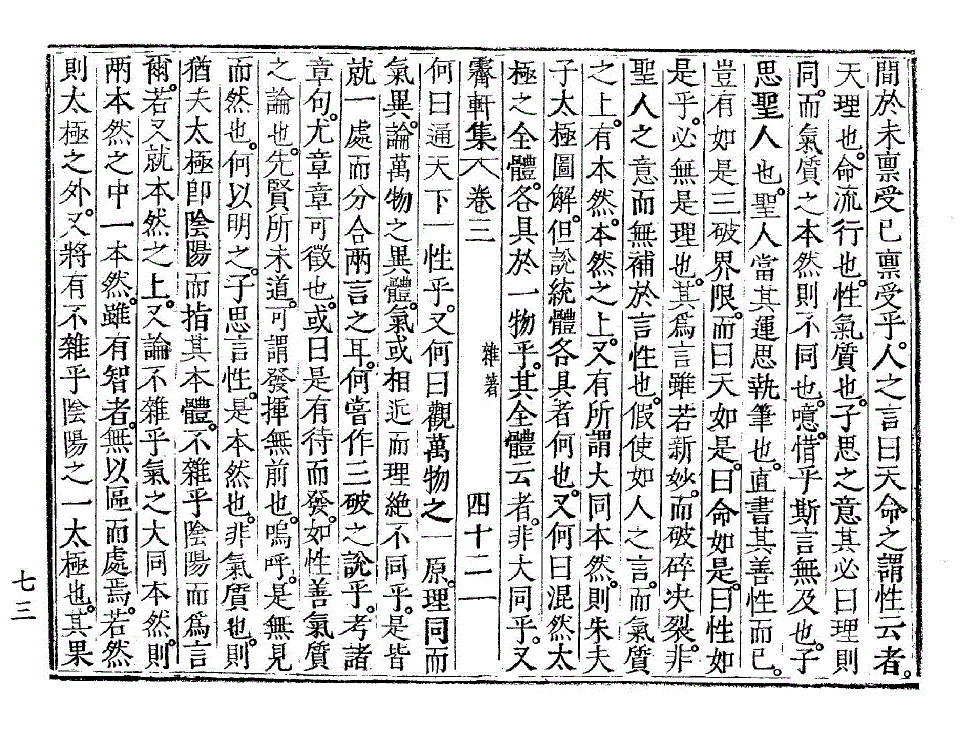 间于未禀受已禀受乎。人之言曰天命之谓性云者。天理也。命流行也。性气质也。子思之意其必曰理则同。而气质之本然则不同也。噫。惜乎斯言无及也。子思圣人也。圣人当其运思执笔也。直书其善性而已。岂有如是三破界限。而曰天如是。曰命如是。曰性如是乎。必无是理也。其为言虽若新妙。而破碎决裂。非圣人之意而无补于言性也。假使如人之言。而气质之上。有本然。本然之上。又有所谓大同本然。则朱夫子太极图解。但说统体各具者何也。又何曰混然太极之全体。各具于一物乎。其全体云者。非大同乎。又何曰通天下一性乎。又何曰观万物之一原。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气或相近而理绝不同乎。是皆就一处而分合两言之耳。何尝作三破之说乎。考诸章句。尤章章可徵也。或曰是有待而发。如性善气质之论也。先贤所未道。可谓发挥无前也。呜呼。是无见而然也。何以明之。子思言性。是本然也。非气质也。则犹夫太极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若又就本然之上。又论不杂乎气之大同本然。则两本然之中一本然。虽有智者。无以区而处焉。若然则太极之外。又将有不杂乎阴阳之一太极也。其果
间于未禀受已禀受乎。人之言曰天命之谓性云者。天理也。命流行也。性气质也。子思之意其必曰理则同。而气质之本然则不同也。噫。惜乎斯言无及也。子思圣人也。圣人当其运思执笔也。直书其善性而已。岂有如是三破界限。而曰天如是。曰命如是。曰性如是乎。必无是理也。其为言虽若新妙。而破碎决裂。非圣人之意而无补于言性也。假使如人之言。而气质之上。有本然。本然之上。又有所谓大同本然。则朱夫子太极图解。但说统体各具者何也。又何曰混然太极之全体。各具于一物乎。其全体云者。非大同乎。又何曰通天下一性乎。又何曰观万物之一原。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气或相近而理绝不同乎。是皆就一处而分合两言之耳。何尝作三破之说乎。考诸章句。尤章章可徵也。或曰是有待而发。如性善气质之论也。先贤所未道。可谓发挥无前也。呜呼。是无见而然也。何以明之。子思言性。是本然也。非气质也。则犹夫太极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若又就本然之上。又论不杂乎气之大同本然。则两本然之中一本然。虽有智者。无以区而处焉。若然则太极之外。又将有不杂乎阴阳之一太极也。其果霁轩集卷之三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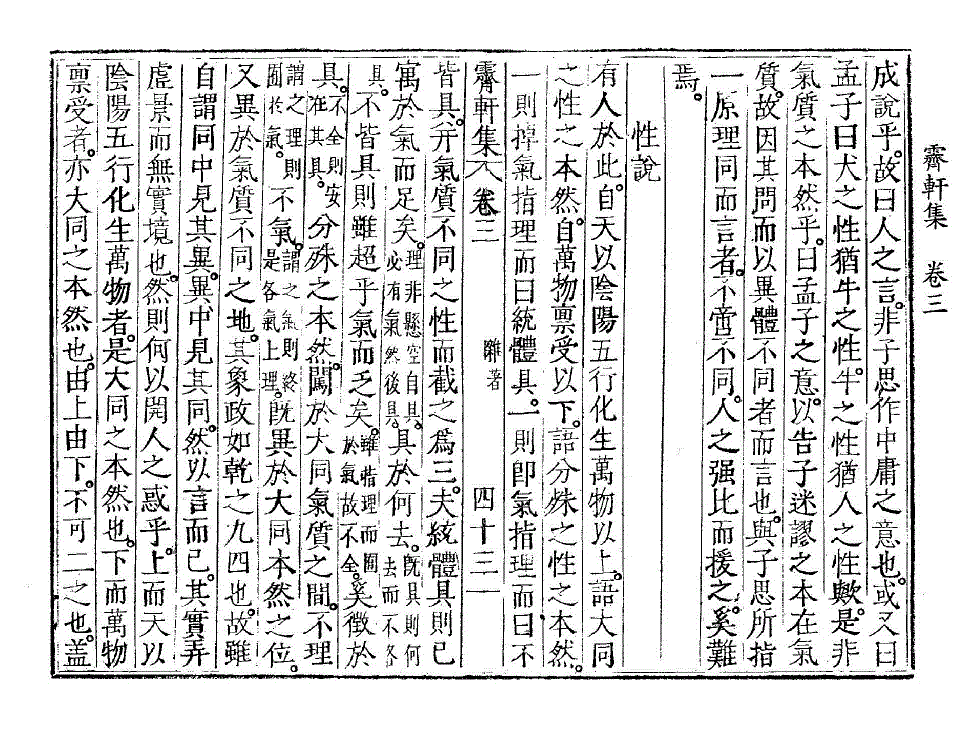 成说乎。故曰人之言。非子思作中庸之意也。或又曰孟子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是非气质之本然乎。曰孟子之意。以告子迷谬之本在气质。故因其问而以异体不同者而言也。与子思所指一原理同而言者。不啻不同。人之强比而援之。奚难焉。
成说乎。故曰人之言。非子思作中庸之意也。或又曰孟子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是非气质之本然乎。曰孟子之意。以告子迷谬之本在气质。故因其问而以异体不同者而言也。与子思所指一原理同而言者。不啻不同。人之强比而援之。奚难焉。性说
有人于此。自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以上。语大同之性之本然。自万物禀受以下。语分殊之性之本然。一则掉气指理而曰统体具。一则即气指理而曰不皆具。并气质不同之性而截之为三。夫统体具则已寓于气而足矣。(理非悬空自具。必有气然后具。)具于何去。(既具则何去而不各具。)不皆具则虽超乎气而乏矣。(虽指理而囿于气故不全。)奚徵于具。(不全则安在其具。)分殊之本然。闯于大同气质之间。不理(谓之理则囿于气。)不气。(谓之气则终是各气上理。)既异于大同本然之位。又异于气质不同之地。其象政如乾之九四也。故虽自谓同中见其异。异中见其同。然以言而已。其实弄虚景而无实境也。然则何以开人之惑乎。上而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者。是大同之本然也。下而万物禀受者。亦大同之本然也。由上由下。不可二之也。盖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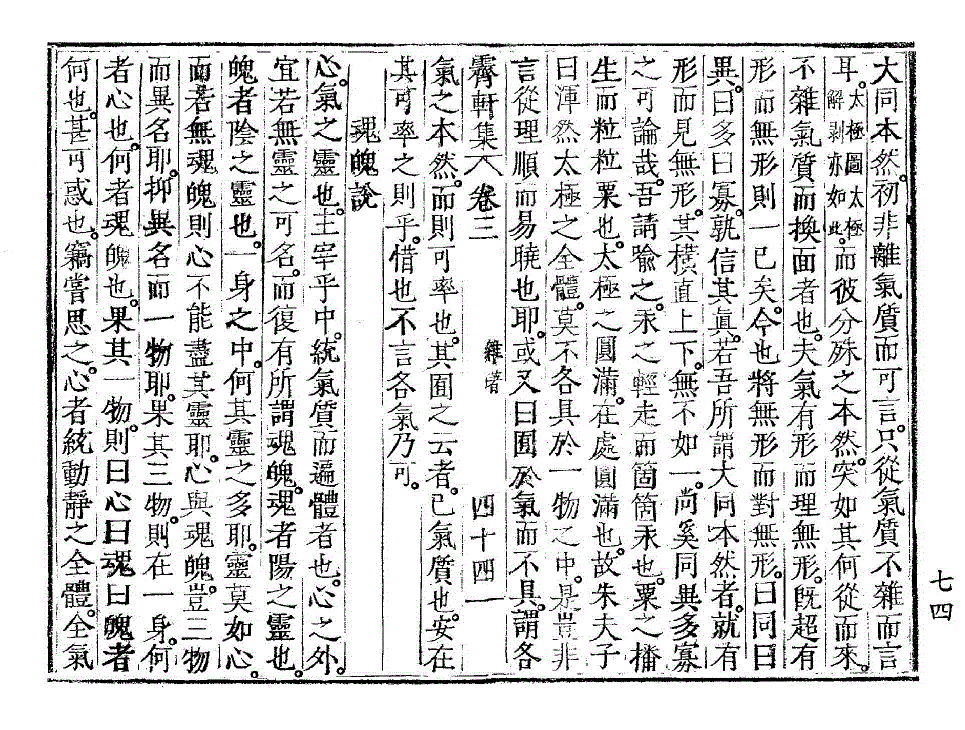 大同本然。初非离气质而可言。只从气质不杂而言耳。(太极图太极解剥亦如此。)而彼分殊之本然。突如其何从而来。不杂气质而换面者也。夫气有形而理无形。既超有形而无形则一已矣。今也将无形而对无形。曰同曰异。曰多曰寡。孰信其真。若吾所谓大同本然者。就有形而见无形。其横直上下。无不如一。尚奚同异多寡之可论哉。吾请喻之。永之轻走而个个永也。粟之播生而粒粒粟也。太极之圆满。在处圆满也。故朱夫子曰浑然太极之全体。莫不各具于一物之中。是岂非言从理顺而易晓也耶。或又曰囿于气而不具。谓各气之本然。而则可率也。其囿之云者。已气质也。安在其可率之则乎。惜也不言各气乃可。
大同本然。初非离气质而可言。只从气质不杂而言耳。(太极图太极解剥亦如此。)而彼分殊之本然。突如其何从而来。不杂气质而换面者也。夫气有形而理无形。既超有形而无形则一已矣。今也将无形而对无形。曰同曰异。曰多曰寡。孰信其真。若吾所谓大同本然者。就有形而见无形。其横直上下。无不如一。尚奚同异多寡之可论哉。吾请喻之。永之轻走而个个永也。粟之播生而粒粒粟也。太极之圆满。在处圆满也。故朱夫子曰浑然太极之全体。莫不各具于一物之中。是岂非言从理顺而易晓也耶。或又曰囿于气而不具。谓各气之本然。而则可率也。其囿之云者。已气质也。安在其可率之则乎。惜也不言各气乃可。魂魄说
心。气之灵也。主宰乎中。统气质而遍体者也。心之外。宜若无灵之可名。而复有所谓魂魄。魂者阳之灵也。魄者阴之灵也。一身之中。何其灵之多耶。灵莫如心。而若无魂魄则心不能尽其灵耶。心与魂魄。岂三物而异名耶。抑异名而一物耶。果其三物。则在一身。何者心也。何者魂魄也。果其一物。则曰心曰魂曰魄者何也。甚可惑也。窃尝思之。心者统动静之全体。全气
霁轩集卷之三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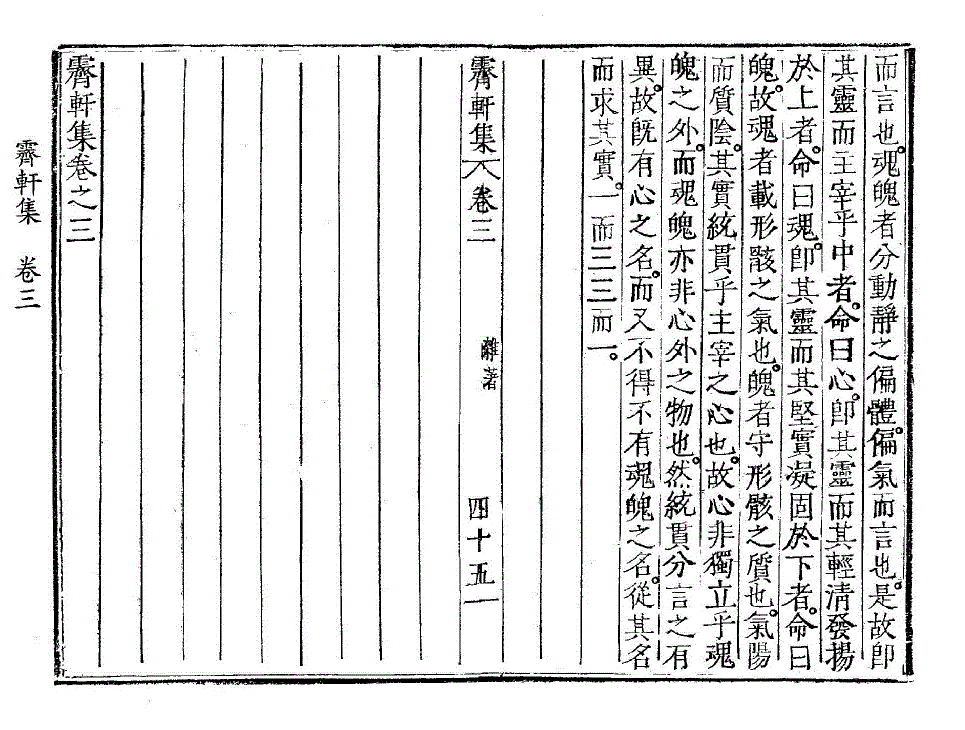 而言也。魂魄者分动静之偏体。偏气而言也。是故即其灵而主宰乎中者。命曰心。即其灵而其轻清发扬于上者。命曰魂。即其灵而其坚实凝固于下者。命曰魄。故魂者载形骸之气也。魄者守形骸之质也。气阳而质阴。其实统贯乎主宰之心也。故心非独立乎魂魄之外。而魂魄亦非心外之物也。然统贯分言之有异。故既有心之名。而又不得不有魂魄之名。从其名而求其实。一而三三而一。
而言也。魂魄者分动静之偏体。偏气而言也。是故即其灵而主宰乎中者。命曰心。即其灵而其轻清发扬于上者。命曰魂。即其灵而其坚实凝固于下者。命曰魄。故魂者载形骸之气也。魄者守形骸之质也。气阳而质阴。其实统贯乎主宰之心也。故心非独立乎魂魄之外。而魂魄亦非心外之物也。然统贯分言之有异。故既有心之名。而又不得不有魂魄之名。从其名而求其实。一而三三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