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x 页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杂著
杂著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68H 页
 看书日录(起癸巳六月二十二日。止七月二十九日。)
看书日录(起癸巳六月二十二日。止七月二十九日。)[癸巳]
[六月]
癸巳六月二十二日。数旬患疟。抛却工课。今日始复看明史成祖纪。上亲征瓦剌。皇太孙从。内侍李谦恃勇。引皇太孙于九龙口。临战几危。上大惊追回。按帝王治国。文事武备。固不可偏废。然人主一身。上奉宗社。下临亿兆。除非敌犯京城。变在呼吸。则不可亲屈万乘之尊。轻冒矢石之危也。彼瓦剌小丑。不过费一将之力。而命驾亲征。深入沙漠。是岂不可已之事耶。况皇太孙年纪尚幼。血气未定。正宜拣选师傅。辅养德性。如欲兼解武事。则亦当谕之以修内攘外之谟。择将饬兵之要。诘戎之政。如是足矣。何必亲御弓马。身犯锋镝而后。始知战场之艰难乎。文皇之身教。已失其道。则九龙之危。又不足责之于内臣也。夫人主少年。志气方强。鲜不驰心于甲兵战阵之间。今帝之所以导太孙者。内习击毬射柳之技。外示玩兵黩武之事。此何足为贻燕之谟哉。○吏部员外郎陈诚使西域备录山川土壤人民物产之异。为行程记上之。诏付史官。按此时日事干戈。兵连沙漠。南北分都。国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68L 页
 力疲弊。奉命之臣。岂可探求远略。以益其穷黩之志乎。昔隋之裴矩撰西域啚记。进之炀帝。使帝慕秦皇汉武之功。卒至中国弊亡。佞臣之启上非心。前后一辙。其亦不仁乎哉。○汉王高煦有罪徙封乐安。按谷王之谋叛。不杀高煦之有罪徒(一作徙)封。俱不免失之太厚。亲王固与外臣不同。死罪以下。宜从八议之法。而至于陈兵谋逆。罪关宗社。则亦不可徒拘私恩。以灭大义。古人有行之者。周讨管蔡是也。谷王之招兵习战。要结蜀援。其反形已具。于此不宜复顾兄弟之谊。况高煦凶悍无比。僭用乘舆。私造兵器。其为后患必矣。何不念宗社之重。割父子之恩。而乃其威罚。不过一褫衣冠。暂絷西华而止。毕竟复授封爵。处于近京。使之益肆异啚。贻祸宗国。既失断义。又非全恩。可惜哉。○ 上命东宫皇太孙周王楚王谒孝陵。问杨士奇以谒陵位次。对曰二王属尊列。稍前两傍。东宫列稍后居中。皇太孙列于东宫之后。而诸皇孙分列两傍。朱某家礼。太约如此。 上曰吾但据己见。书其位次。送出片楮。正与士奇言合。命行之如仪。按此恐非也。朱子家礼。只就士夫家祭礼。分宗支定序次而已。不可混用于帝王之家也。东宫序虽卑。乃贰君也。二王
力疲弊。奉命之臣。岂可探求远略。以益其穷黩之志乎。昔隋之裴矩撰西域啚记。进之炀帝。使帝慕秦皇汉武之功。卒至中国弊亡。佞臣之启上非心。前后一辙。其亦不仁乎哉。○汉王高煦有罪徙封乐安。按谷王之谋叛。不杀高煦之有罪徒(一作徙)封。俱不免失之太厚。亲王固与外臣不同。死罪以下。宜从八议之法。而至于陈兵谋逆。罪关宗社。则亦不可徒拘私恩。以灭大义。古人有行之者。周讨管蔡是也。谷王之招兵习战。要结蜀援。其反形已具。于此不宜复顾兄弟之谊。况高煦凶悍无比。僭用乘舆。私造兵器。其为后患必矣。何不念宗社之重。割父子之恩。而乃其威罚。不过一褫衣冠。暂絷西华而止。毕竟复授封爵。处于近京。使之益肆异啚。贻祸宗国。既失断义。又非全恩。可惜哉。○ 上命东宫皇太孙周王楚王谒孝陵。问杨士奇以谒陵位次。对曰二王属尊列。稍前两傍。东宫列稍后居中。皇太孙列于东宫之后。而诸皇孙分列两傍。朱某家礼。太约如此。 上曰吾但据己见。书其位次。送出片楮。正与士奇言合。命行之如仪。按此恐非也。朱子家礼。只就士夫家祭礼。分宗支定序次而已。不可混用于帝王之家也。东宫序虽卑。乃贰君也。二王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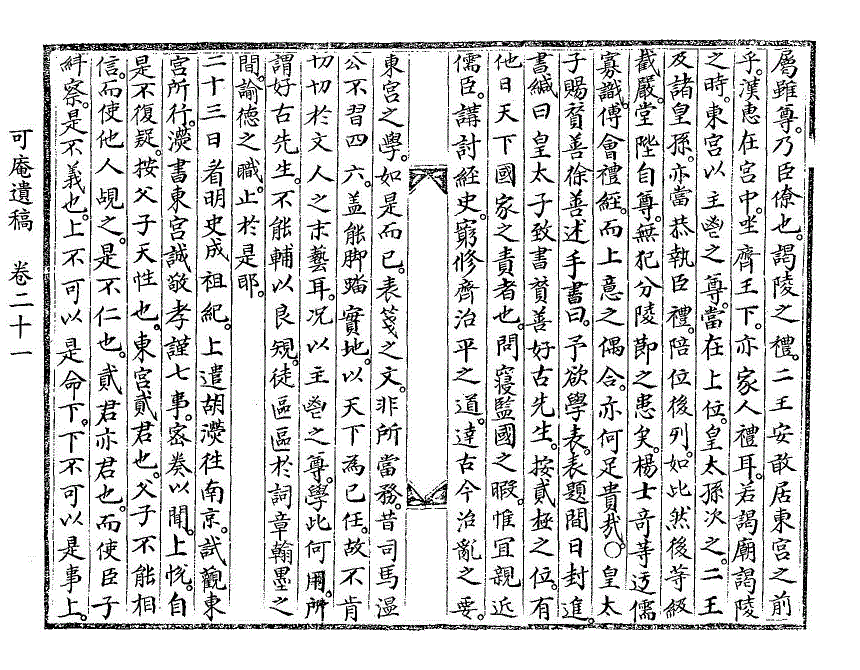 属虽尊。乃臣僚也。谒陵之礼。二王安敢居东宫之前乎。汉惠在宫中。坐齐王下。亦家人礼耳。若谒庙谒陵之时。东宫以主鬯之尊。当在上位。皇太孙次之。二王及诸皇孙。亦当恭执臣礼。陪位后列。如此然后等级截严。堂陛自尊。无犯分陵节之患矣。杨士奇等迂儒寡识。傅会礼经。而上意之偶合。亦何足贵哉。○皇太子赐赞善徐善述手书曰。予欲学表。表题间日封进。书缄曰皇太子致书赞善好古先生。按贰极之位。有他日天下国家之责者也。问寝监国之暇。惟宜亲近儒臣。讲讨经史。穷修齐治平之道。达古今治乱之要。东宫之学。如是而已。表笺之文。非所当务。昔司马温公不习四六。盖能脚踏实地。以天下为己任。故不肯切切于文人之末艺耳。况以主鬯之尊。学此何用。所谓好古先生。不能辅以良规。徒区区于词章翰墨之间。谕德之职。止于是耶。
属虽尊。乃臣僚也。谒陵之礼。二王安敢居东宫之前乎。汉惠在宫中。坐齐王下。亦家人礼耳。若谒庙谒陵之时。东宫以主鬯之尊。当在上位。皇太孙次之。二王及诸皇孙。亦当恭执臣礼。陪位后列。如此然后等级截严。堂陛自尊。无犯分陵节之患矣。杨士奇等迂儒寡识。傅会礼经。而上意之偶合。亦何足贵哉。○皇太子赐赞善徐善述手书曰。予欲学表。表题间日封进。书缄曰皇太子致书赞善好古先生。按贰极之位。有他日天下国家之责者也。问寝监国之暇。惟宜亲近儒臣。讲讨经史。穷修齐治平之道。达古今治乱之要。东宫之学。如是而已。表笺之文。非所当务。昔司马温公不习四六。盖能脚踏实地。以天下为己任。故不肯切切于文人之末艺耳。况以主鬯之尊。学此何用。所谓好古先生。不能辅以良规。徒区区于词章翰墨之间。谕德之职。止于是耶。二十三日看明史成祖纪。上遣胡濙往南京。试观东宫所行。濙书东宫诚敬孝谨七事。密奏以闻。上悦。自是不复疑。按父子天性也。东宫贰君也。父子不能相信。而使他人觇之。是不仁也。贰君亦君也。而使臣子纠察。是不义也。上不可以是命下。下不可以是事上。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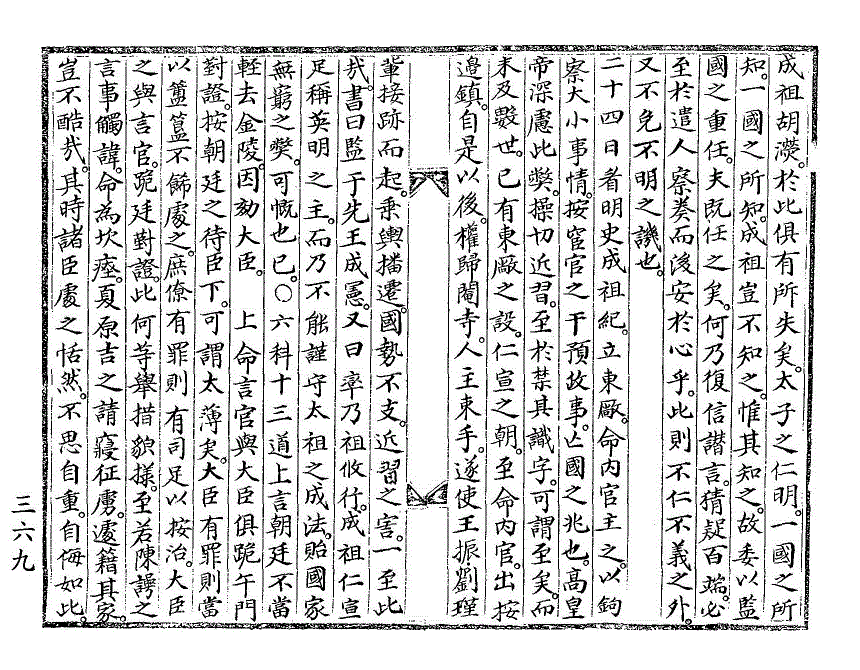 成祖胡濙。于此俱有所失矣。太子之仁明。一国之所知。一国之所知。成祖岂不知之。惟其知之。故委以监国之重任。夫既任之矣。何乃复信谮言。猜疑百端。必至于遣人察奏而后安于心乎。此则不仁不义之外。又不免不明之讥也。
成祖胡濙。于此俱有所失矣。太子之仁明。一国之所知。一国之所知。成祖岂不知之。惟其知之。故委以监国之重任。夫既任之矣。何乃复信谮言。猜疑百端。必至于遣人察奏而后安于心乎。此则不仁不义之外。又不免不明之讥也。二十四日看明史成祖纪。立东厂。命内官主之。以钩察大小事情。按宦官之干预政事。亡国之兆也。高皇帝深虑此弊。操切近习。至于禁其识字。可谓至矣。而未及数世。已有东厂之设。仁宣之朝。至命内官。出按边镇。自是以后。权归阉寺。人主束手。遂使王振,刘瑾辈接迹而起。乘舆播迁。国势不支。近习之害。一至此哉。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又曰率乃祖攸行。成祖仁宣足称英明之主。而乃不能谨守太祖之成法。贻国家无穷之弊。可慨也已。○六科十三道上言朝廷不当轻去金陵。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与大臣俱跪午门对證。按朝廷之待臣下。可谓太薄矣。大臣有罪则当以簠簋不饰处之。庶僚有罪则有司足以按治。大臣之与言官。跪廷对證。此何等举措貌㨾。至若陈谔之言事触讳。命为坎瘗。夏原吉之请寝征虏。遽籍其家。岂不酷哉。其时诸臣处之恬然。不思自重。自侮如此。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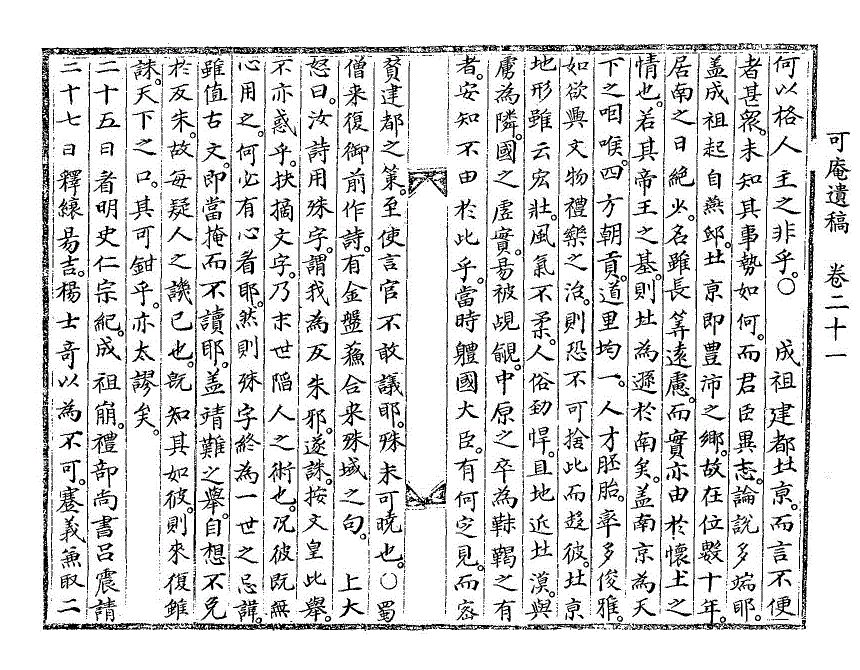 何以格人主之非乎。○ 成祖建都北京。而言不便者甚众。未知其事势如何。而君臣异志。论说多端耶。盖成祖起自燕邸。北京即礼沛之乡。故在位数十年。居南之日绝少。名虽长算远虑。而实亦由于怀土之情也。若其帝王之基。则北为逊于南矣。盖南京为天下之咽喉。四方朝贡。道里均一。人才胚胎。率多俊雅。如欲兴文物礼乐之治。则恐不可舍此而趍彼。北京地形虽云宏壮。风气不柔。人俗劲悍。且地近北漠。与虏为邻。国之虚实。易被觇觎。中原之卒为靺鞨之有者。安知不由于此乎。当时体国大臣。有何定见。而密赞建都之策。至使言官不敢议耶。殊未可晓也。○蜀僧来复御前作诗。有金盘苏合来殊域之句。 上大怒曰。汝诗用殊字。谓我为反朱邪。遂诛。按文皇此举。不亦惑乎。抉摘文字。乃末世陷人之术也。况彼既无心用之。何必有心看耶。然则殊字终为一世之忌讳。虽值古文。即当掩而不读耶。盖靖难之举。自想不免于反朱。故每疑人之讥己也。既知其如彼。则来复虽诛。天下之口。其可钳乎。亦太谬矣。
何以格人主之非乎。○ 成祖建都北京。而言不便者甚众。未知其事势如何。而君臣异志。论说多端耶。盖成祖起自燕邸。北京即礼沛之乡。故在位数十年。居南之日绝少。名虽长算远虑。而实亦由于怀土之情也。若其帝王之基。则北为逊于南矣。盖南京为天下之咽喉。四方朝贡。道里均一。人才胚胎。率多俊雅。如欲兴文物礼乐之治。则恐不可舍此而趍彼。北京地形虽云宏壮。风气不柔。人俗劲悍。且地近北漠。与虏为邻。国之虚实。易被觇觎。中原之卒为靺鞨之有者。安知不由于此乎。当时体国大臣。有何定见。而密赞建都之策。至使言官不敢议耶。殊未可晓也。○蜀僧来复御前作诗。有金盘苏合来殊域之句。 上大怒曰。汝诗用殊字。谓我为反朱邪。遂诛。按文皇此举。不亦惑乎。抉摘文字。乃末世陷人之术也。况彼既无心用之。何必有心看耶。然则殊字终为一世之忌讳。虽值古文。即当掩而不读耶。盖靖难之举。自想不免于反朱。故每疑人之讥己也。既知其如彼。则来复虽诛。天下之口。其可钳乎。亦太谬矣。二十五日看明史仁宗纪。成祖崩。礼部尚书吕震请二十七日释缞易吉。杨士奇以为不可。蹇义兼取二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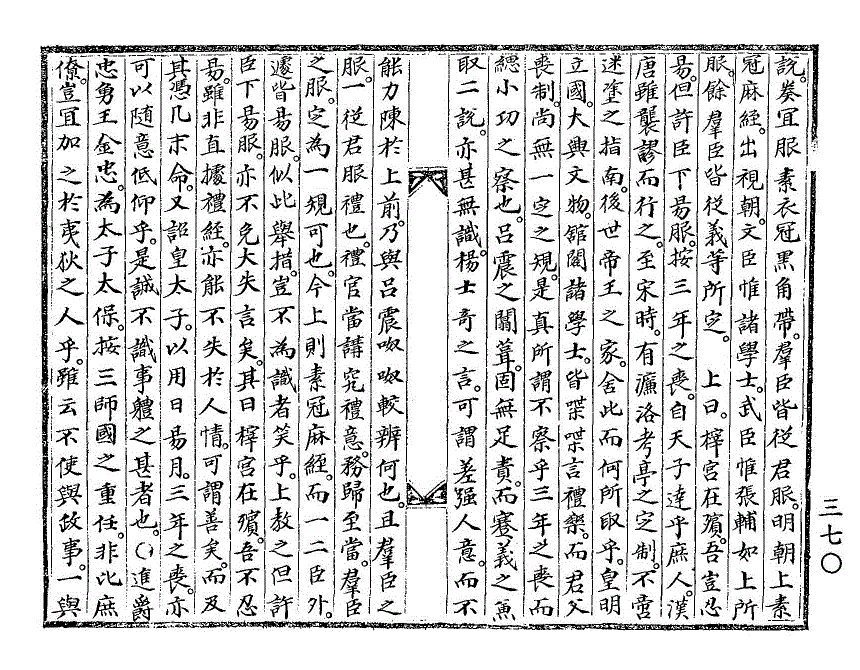 说。奏宜服素衣冠黑角带。群臣皆从君服。明朝上素冠麻绖。出视朝。文臣惟诸学士。武臣惟张辅如上所服。馀群臣皆从义等所定。 上曰。梓宫在殡。吾岂忍易。但许臣下易服。按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乎庶人。汉唐虽袭谬而行之。至宋时。有濂洛考亭之定制。不啻迷涂之指南。后世帝王之家。舍此而何所取乎。皇明立国。大兴文物。馆阁诸学士。皆喋喋言礼乐。而君父丧制。尚无一定之规。是真所谓不察乎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也。吕震之阘葺。固无足责。而蹇义之兼取二说。亦甚无识。杨士奇之言。可谓差强人意。而不能力陈于上前。乃与吕震呶呶较辨何也。且群臣之服。一从君服礼也。礼官当讲究礼意。务归至当。群臣之服。定为一规可也。今上则素冠麻绖。而一二臣外。遽皆易服。似此举措。岂不为识者笑乎。上教之但许臣下易服。亦不免大失言矣。其日梓宫在殡。吾不忍易。虽非直据礼经。亦能不失于人情。可谓善矣。而及其凭几末命。又诏皇太子。以用日易月。三年之丧。亦可以随意低仰乎。是诚不识事体之甚者也。○进爵忠勇王金忠。为太子太保。按三师国之重任。非比庶僚。岂宜加之于夷狄之人乎。虽云不使与政事。一与
说。奏宜服素衣冠黑角带。群臣皆从君服。明朝上素冠麻绖。出视朝。文臣惟诸学士。武臣惟张辅如上所服。馀群臣皆从义等所定。 上曰。梓宫在殡。吾岂忍易。但许臣下易服。按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乎庶人。汉唐虽袭谬而行之。至宋时。有濂洛考亭之定制。不啻迷涂之指南。后世帝王之家。舍此而何所取乎。皇明立国。大兴文物。馆阁诸学士。皆喋喋言礼乐。而君父丧制。尚无一定之规。是真所谓不察乎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也。吕震之阘葺。固无足责。而蹇义之兼取二说。亦甚无识。杨士奇之言。可谓差强人意。而不能力陈于上前。乃与吕震呶呶较辨何也。且群臣之服。一从君服礼也。礼官当讲究礼意。务归至当。群臣之服。定为一规可也。今上则素冠麻绖。而一二臣外。遽皆易服。似此举措。岂不为识者笑乎。上教之但许臣下易服。亦不免大失言矣。其日梓宫在殡。吾不忍易。虽非直据礼经。亦能不失于人情。可谓善矣。而及其凭几末命。又诏皇太子。以用日易月。三年之丧。亦可以随意低仰乎。是诚不识事体之甚者也。○进爵忠勇王金忠。为太子太保。按三师国之重任。非比庶僚。岂宜加之于夷狄之人乎。虽云不使与政事。一与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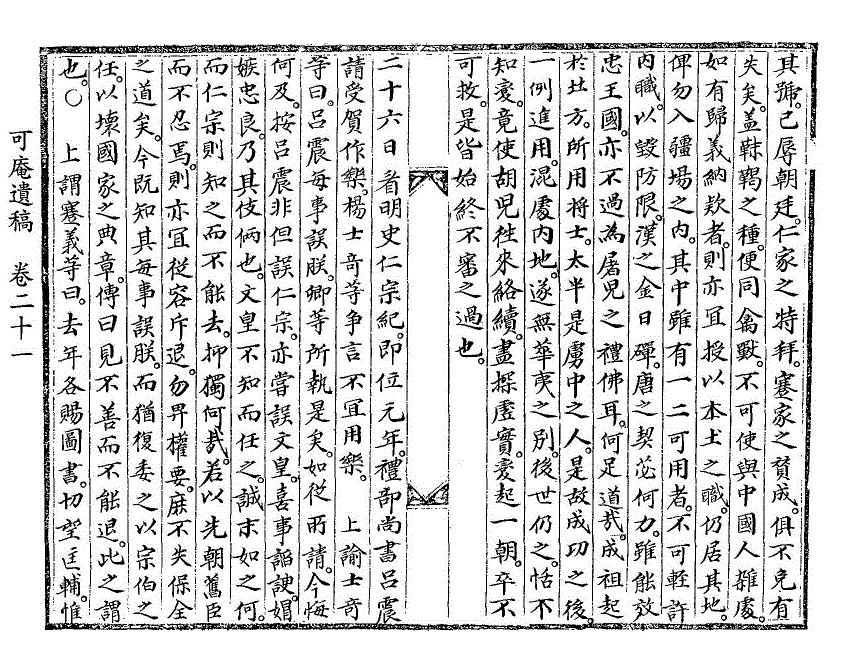 其号。已辱朝廷。仁家之特拜。蹇家之赞成。俱不免有失矣。盖靺鞨之种。便同禽兽。不可使与中国人杂处。如有归义纳款者。则亦宜授以本土之职。仍居其地。俾勿入疆埸之内。其中虽有一二可用者。不可轻许内职。以毁防限。汉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虽能效忠王国。亦不过为屠儿之礼佛耳。何足道哉。成祖起于北方。所用将士。太半是虏中之人。是故成功之后。一例进用。混处内地。遂无华夷之别。后世仍之。恬不知变。竟使胡儿往来络续。尽探虚实。变起一朝。卒不可救。是皆始终不审之过也。
其号。已辱朝廷。仁家之特拜。蹇家之赞成。俱不免有失矣。盖靺鞨之种。便同禽兽。不可使与中国人杂处。如有归义纳款者。则亦宜授以本土之职。仍居其地。俾勿入疆埸之内。其中虽有一二可用者。不可轻许内职。以毁防限。汉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虽能效忠王国。亦不过为屠儿之礼佛耳。何足道哉。成祖起于北方。所用将士。太半是虏中之人。是故成功之后。一例进用。混处内地。遂无华夷之别。后世仍之。恬不知变。竟使胡儿往来络续。尽探虚实。变起一朝。卒不可救。是皆始终不审之过也。二十六日看明史仁宗纪。即位元年。礼部尚书吕震请受贺作乐。杨士奇等争言不宜用乐。 上谕士奇等曰。吕震每事误朕。卿等所执是矣。如从所请。今悔何及。按吕震非但误仁宗。亦尝误文皇。喜事谄谀。媢嫉忠良。乃其伎俩也。文皇不知而任之。诚末如之何。而仁宗则知之而不能去。抑独何哉。若以先朝旧臣而不忍焉。则亦宜从容斥退。勿畀权要。庶不失保全之道矣。今既知其每事误朕。而犹复委之以宗伯之任。以坏国家之典章。传曰见不善而不能退。此之谓也。○ 上谓蹇义等曰。去年各赐图书。切望匡辅。惟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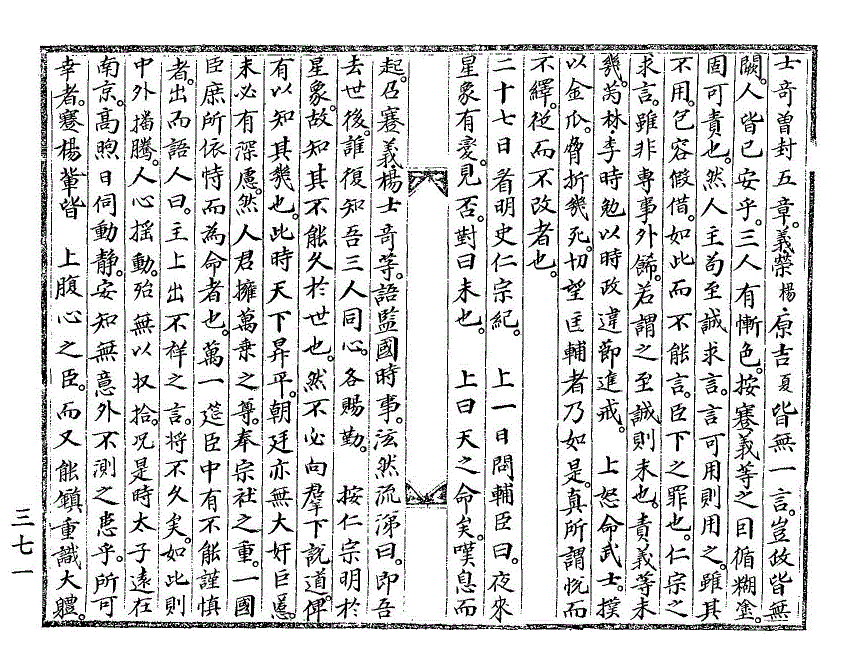 士奇曾封五章。义,荣(杨),原吉(夏)皆无一言。岂政皆无阙。人皆已安乎。三人有惭色。按蹇义等之因循糊涂。固可责也。然人主苟至诚求言。言可用则用之。虽其不用。包容假借。如此而不能言。臣下之罪也。仁宗之求言。虽非专事外饰。若谓之至诚则未也。责义等未几。芮林,李时勉以时政违节进戒。 上怒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几死。切望匡辅者乃如是。真所谓悦而不绎。从而不改者也。
士奇曾封五章。义,荣(杨),原吉(夏)皆无一言。岂政皆无阙。人皆已安乎。三人有惭色。按蹇义等之因循糊涂。固可责也。然人主苟至诚求言。言可用则用之。虽其不用。包容假借。如此而不能言。臣下之罪也。仁宗之求言。虽非专事外饰。若谓之至诚则未也。责义等未几。芮林,李时勉以时政违节进戒。 上怒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几死。切望匡辅者乃如是。真所谓悦而不绎。从而不改者也。二十七日看明史仁宗纪。 上一日问辅臣曰。夜来星象有变。见否。对曰未也。 上曰天之命矣。叹息而起。召蹇义,杨士奇等。语监国时事。泫然流涕曰。即吾去世后。谁复知吾三人同心。各赐勤。 按仁宗明于星象。故知其不能久于世也。然不必向群下说道。俾有以知其几也。此时天下升平。朝廷亦无大奸巨慝。未必有深虑。然人君拥万乘之尊。奉宗社之重。一国臣庶所依恃而为命者也。万一筵臣中有不能谨慎者。出而语人曰。主上出不祥之言。将不久矣。如此则中外播腾。人心摇动。殆无以收拾。况是时太子远在南京。高煦日伺动静。安知无意外不测之患乎。所可幸者。蹇杨辈皆 上腹心之臣。而又能镇重识大体。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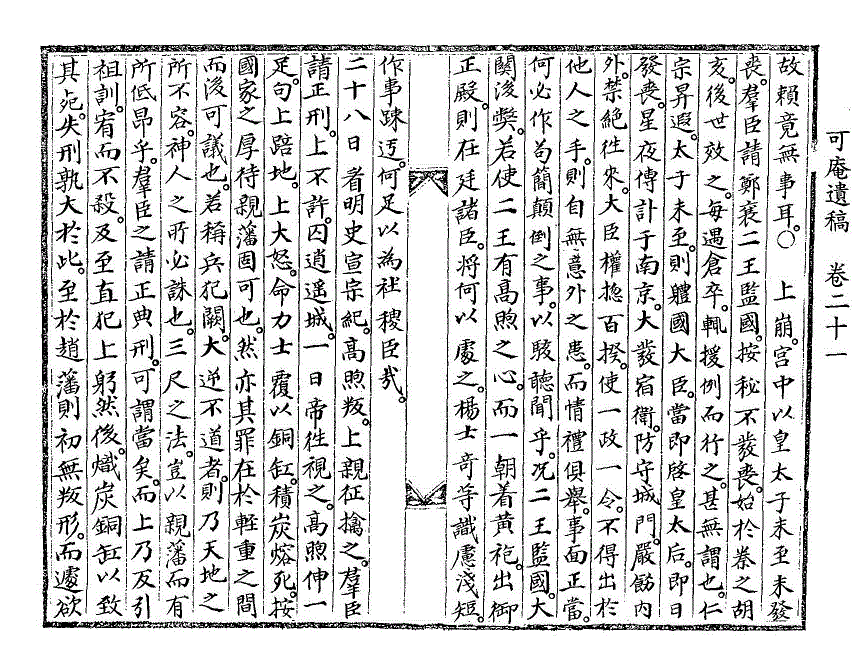 故赖竟无事耳。○ 上崩。宫中以皇太子未至未发丧。群臣请郑襄二王监国。按秘不发丧。始于秦之胡亥。后世效之。每遇仓卒。辄援例而行之。甚无谓也。仁宗升遐。太子未至。则体国大臣。当即启皇太后。即日发丧。星夜传讣于南京。大发宿卫。防守城门。严饬内外。禁绝往来。大臣权揔百揆。使一政一令。不得出于他人之手。则自无意外之患。而情礼俱举。事面正当。何必作苟简颠倒之事。以骇听闻乎。况二王监国。大关后弊。若使二王有高煦之心。而一朝着黄袍。出御正殿。则在廷诸臣。将何以处之。杨士奇等识虑浅短。作事疏迂。何足以为社稷臣哉。
故赖竟无事耳。○ 上崩。宫中以皇太子未至未发丧。群臣请郑襄二王监国。按秘不发丧。始于秦之胡亥。后世效之。每遇仓卒。辄援例而行之。甚无谓也。仁宗升遐。太子未至。则体国大臣。当即启皇太后。即日发丧。星夜传讣于南京。大发宿卫。防守城门。严饬内外。禁绝往来。大臣权揔百揆。使一政一令。不得出于他人之手。则自无意外之患。而情礼俱举。事面正当。何必作苟简颠倒之事。以骇听闻乎。况二王监国。大关后弊。若使二王有高煦之心。而一朝着黄袍。出御正殿。则在廷诸臣。将何以处之。杨士奇等识虑浅短。作事疏迂。何足以为社稷臣哉。二十八日看明史宣宗纪。高煦叛。上亲征擒之。群臣请正刑。上不许。囚逍遥城。一日帝往视之。高煦伸一足。句上踣地。上大怒。命力士覆以铜缸。积炭熔死。按国家之厚待亲藩固可也。然亦其罪在于轻重之间而后可议也。若称兵犯阙。大逆不道者。则乃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必诛也。三尺之法。岂以亲藩而有所低昂乎。群臣之请正典刑。可谓当矣。而上乃反引祖训。宥而不杀。及至直犯上躬然后。炽炭铜缸以致其死。失刑孰大于此。至于赵藩则初无叛形。而遽欲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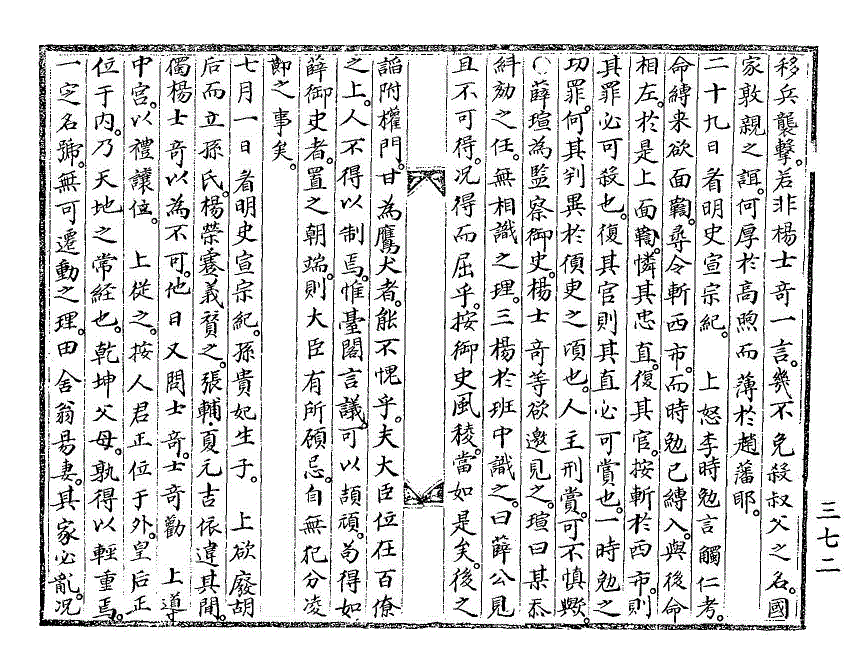 移兵袭击。若非杨士奇一言。几不免杀叔父之名。国家敦亲之谊。何厚于高煦而薄于赵藩耶。
移兵袭击。若非杨士奇一言。几不免杀叔父之名。国家敦亲之谊。何厚于高煦而薄于赵藩耶。二十九日看明史宣宗纪。 上怒李时勉言触仁考。命缚来欲面鞫。寻令斩西市。而时勉已缚入。与后命相左。于是上面鞫。怜其忠直。复其官。按斩于西市。则其罪必可杀也。复其官则其直必可赏也。一时勉之功罪。何其判异于须臾之顷也。人主刑赏。可不慎欤。○薛瑄为监察御史。杨士奇等欲邀见之。瑄曰某忝纠劾之任。无相识之理。三杨于班中识之。曰薛公见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按御史风棱。当如是矣。后之谄附权门甘为鹰犬者。能不愧乎。夫大臣位在百僚之上。人不得以制焉。惟台阁言议。可以颉颃。苟得如薛御史者。置之朝端。则大臣有所顾忌。自无犯分凌节之事矣。
[七月]
七月一日看明史宣宗纪。孙贵妃生子。 上欲废胡后而立孙氏。杨荣,蹇义赞之。张辅,夏元吉依违其间。独杨士奇以为不可。他日又问士奇。士奇劝 上导中宫。以礼让位。 上从之。按人君正位于外。皇后正位于内。乃天地之常经也。乾坤父母。孰得以轻重焉。一定名号。无可迁动之理。田舍翁易妻。其家必乱。况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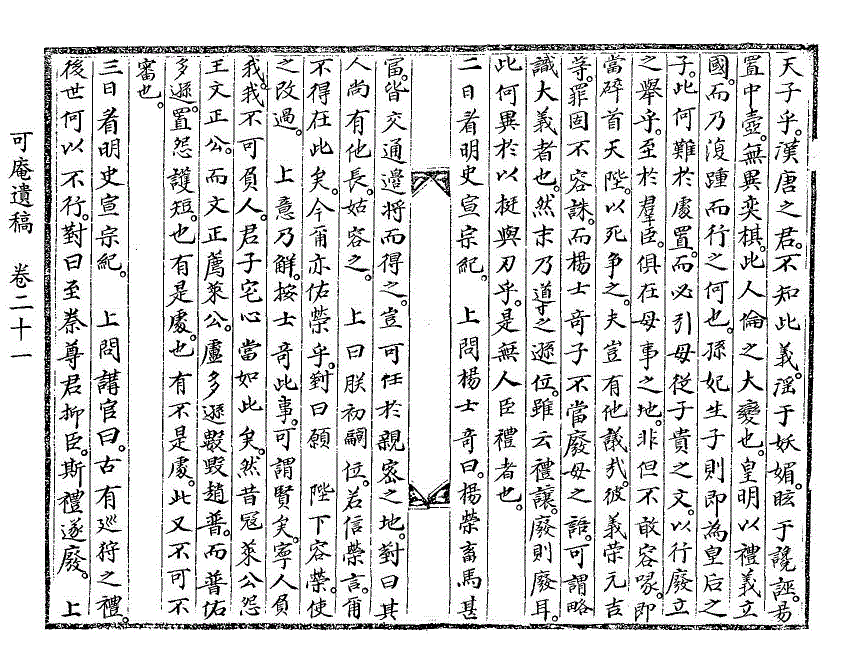 天子乎。汉唐之君。不知此义。淫于妖媚。眩于谗诬。易置中壸。无异奕棋。此人伦之大变也。皇明以礼义立国。而乃复踵而行之何也。孙妃生子则即为皇后之子。此何难于处置。而必引母从子贵之文。以行废立之举乎。至于群臣。俱在母事之地。非但不敢容喙。即当碎首天陛。以死争之。夫岂有他议哉。彼义,荣,元吉等。罪固不容诛。而杨士奇子不当废母之语。可谓略识大义者也。然末乃导之逊位。虽云礼让。废则废耳。此何异于以挺与刃乎。是无人臣礼者也。
天子乎。汉唐之君。不知此义。淫于妖媚。眩于谗诬。易置中壸。无异奕棋。此人伦之大变也。皇明以礼义立国。而乃复踵而行之何也。孙妃生子则即为皇后之子。此何难于处置。而必引母从子贵之文。以行废立之举乎。至于群臣。俱在母事之地。非但不敢容喙。即当碎首天陛。以死争之。夫岂有他议哉。彼义,荣,元吉等。罪固不容诛。而杨士奇子不当废母之语。可谓略识大义者也。然末乃导之逊位。虽云礼让。废则废耳。此何异于以挺与刃乎。是无人臣礼者也。二日看明史宣宗纪。 上问杨士奇曰。杨荣畜马甚富。皆交通边将而得之。岂可任于亲密之地。对曰其人尚有他长。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信荣言。尔不得在此矣。今尔亦佑荣乎。对曰愿 陛下容荣。使之改过。 上意乃解。按士奇此事。可谓贤矣。宁人负我。我不可负人。君子宅心当如此矣。然昔寇莱公怨王文正公。而文正荐莱公。卢多逊数毁赵普。而普佑多逊。置怨护短。也有是处。也有不是处。此又不可不审也。
三日看明史宣宗纪。 上问讲官曰。古有巡狩之礼。后世何以不行。对曰至秦尊君抑臣。斯礼遂废。 上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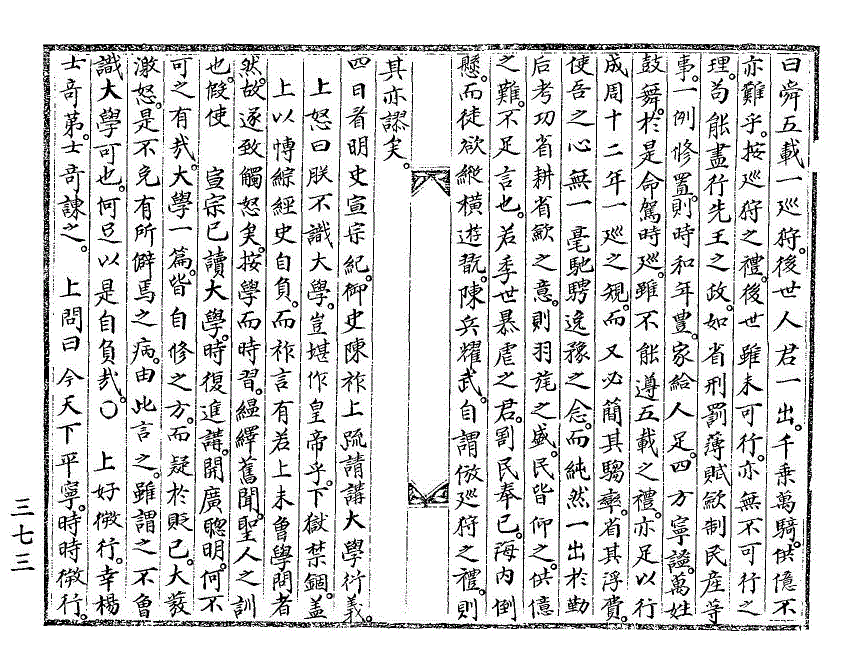 曰舜五载一巡狩。后世人君一出。千乘万骑。供亿不亦难乎。按巡狩之礼。后世虽未可行。亦无不可行之理。苟能尽行先王之政。如省刑罚薄赋敛制民产等事。一例修置。则时和年礼。家给人足。四方宁谧。万姓鼓舞。于是命驾时巡。虽不能遵五载之礼。亦足以行成周十二年一巡之规。而又必简其驺率。省其浮费。使吾之心无一毫驰骋逸豫之念。而纯然一出于勤后考功省耕省敛之意。则羽旄之盛。民皆仰之。供亿之难。不足言也。若季世暴虐之君。割民奉己。海内倒悬。而徒欲纵横游玩。陈兵耀武。自谓仿巡狩之礼。则其亦谬矣。
曰舜五载一巡狩。后世人君一出。千乘万骑。供亿不亦难乎。按巡狩之礼。后世虽未可行。亦无不可行之理。苟能尽行先王之政。如省刑罚薄赋敛制民产等事。一例修置。则时和年礼。家给人足。四方宁谧。万姓鼓舞。于是命驾时巡。虽不能遵五载之礼。亦足以行成周十二年一巡之规。而又必简其驺率。省其浮费。使吾之心无一毫驰骋逸豫之念。而纯然一出于勤后考功省耕省敛之意。则羽旄之盛。民皆仰之。供亿之难。不足言也。若季世暴虐之君。割民奉己。海内倒悬。而徒欲纵横游玩。陈兵耀武。自谓仿巡狩之礼。则其亦谬矣。四日看明史宣宗纪。御史陈祚上疏请讲大学衍义。 上怒曰朕不识大学。岂堪作皇帝乎。下狱禁锢。盖 上以博综经史自负。而祚言有若上未曾学问者然。故遂致触怒矣。按学而时习。缊绎旧闻。圣人之训也。假使 宣宗已读大学。时复进讲。开广聪明。何不可之有哉。大学一篇。皆自修之方。而疑于贬己。大发激怒。是不免有所僻焉之病。由此言之。虽谓之不曾识大学可也。何足以是自负哉。○ 上好微行。幸杨士奇第。士奇谏之。 上问曰今天下平宁。时时微行。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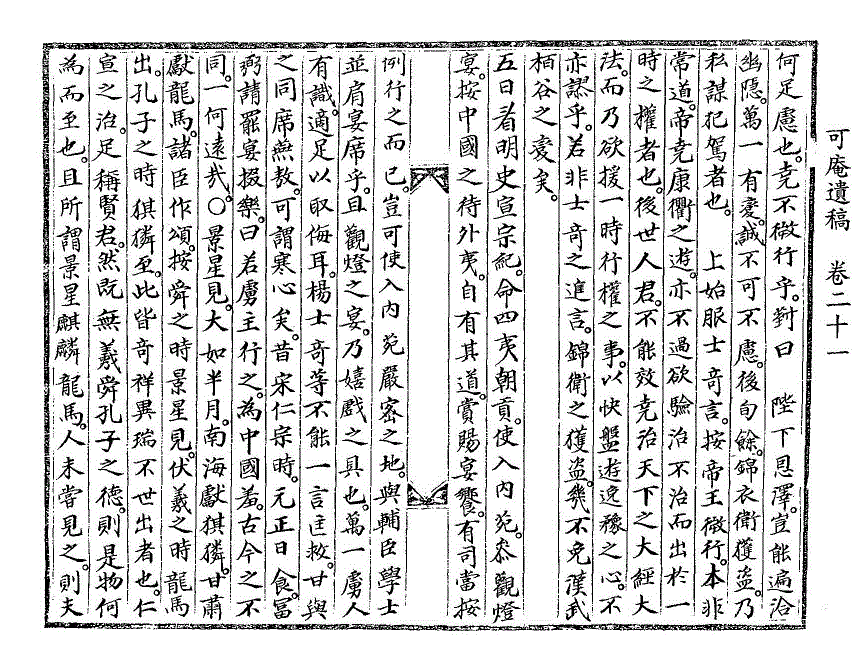 何足虑也。尧不微行乎。对曰 陛下恩泽。岂能遍洽幽隐。万一有变。诚不可不虑。后旬馀。锦衣卫获盗。乃私谋犯驾者也。 上始服士奇言。按帝王微行。本非常道。帝尧康衢之游。亦不过欲验治不治而出于一时之权者也。后世人君。不能效尧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乃欲援一时行权之事。以快盘游逸豫之心。不亦谬乎。若非士奇之进言。锦卫之获盗。几不免汉武柏谷之变矣。
何足虑也。尧不微行乎。对曰 陛下恩泽。岂能遍洽幽隐。万一有变。诚不可不虑。后旬馀。锦衣卫获盗。乃私谋犯驾者也。 上始服士奇言。按帝王微行。本非常道。帝尧康衢之游。亦不过欲验治不治而出于一时之权者也。后世人君。不能效尧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乃欲援一时行权之事。以快盘游逸豫之心。不亦谬乎。若非士奇之进言。锦卫之获盗。几不免汉武柏谷之变矣。五日看明史宣宗纪。命四夷朝贡。使入内苑。参观灯宴。按中国之待外夷。自有其道。赏赐宴飨。有司当按例行之而已。岂可使入内苑严密之地。与辅臣学士并肩宴席乎。且观灯之宴。乃嬉戏之具也。万一虏人有识。适足以取侮耳。杨士奇等不能一言匡救。甘与之同席燕敖。可谓寒心矣。昔宋仁宗时。元正日食。富弼请罢宴掇乐。曰若虏主行之。为中国羞。古今之不同。一何远哉。○景星见。大如半月。南海献猉獜。甘肃献龙马。诸臣作颂。按舜之时景星见。伏羲之时龙马出。孔子之时猉獜至。此皆奇祥异瑞不世出者也。仁宣之治。足称贤君。然既无羲舜孔子之德。则是物何为而至也。且所谓景星麒麟龙马。人未尝见之。则夫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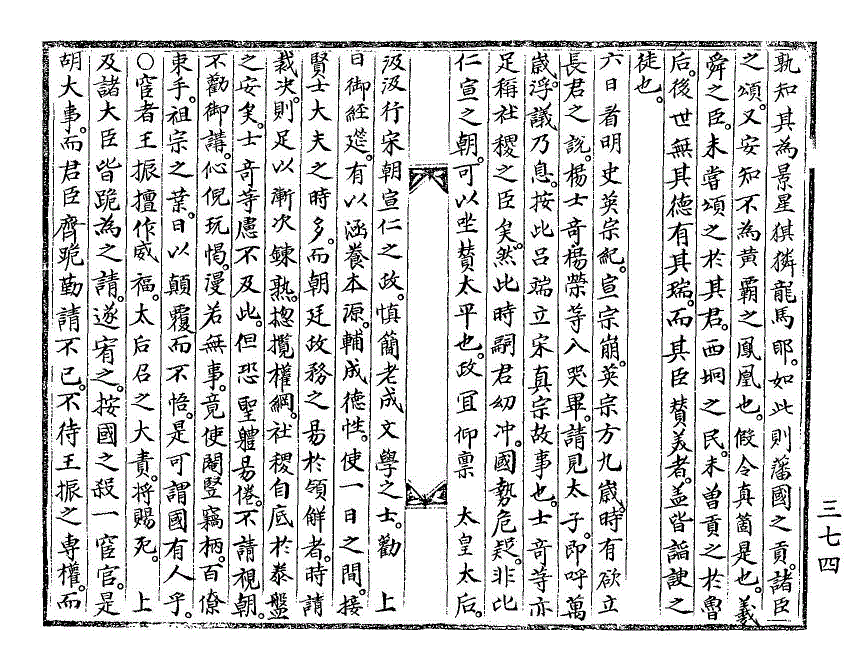 孰知其为景星猉獜龙马耶。如此则藩国之贡。诸臣之颂。又安知不为黄霸之凤凰也。假令真个是也。羲舜之臣。未尝颂之于其君。西坰之民。未曾贡之于鲁后。后世无其德有其瑞。而其臣赞美者。盖皆谄谀之徒也。
孰知其为景星猉獜龙马耶。如此则藩国之贡。诸臣之颂。又安知不为黄霸之凤凰也。假令真个是也。羲舜之臣。未尝颂之于其君。西坰之民。未曾贡之于鲁后。后世无其德有其瑞。而其臣赞美者。盖皆谄谀之徒也。六日看明史英宗纪。宣宗崩。英宗方九岁。时有欲立长君之说。杨士奇,杨荣等入哭毕。请见太子。即呼万岁。浮议乃息。按此吕端立宋真宗故事也。士奇等亦足称社稷之臣矣。然此时嗣君幼冲。国势危疑。非比仁宣之朝。可以坐赞太平也。政宜仰禀 太皇太后。汲汲行宋朝宣仁之政。慎简老成文学之士。劝 上日御经筵。有以涵养本源。辅成德性。使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而朝廷政务之易于领解者。时请裁决。则足以渐次鍊熟。揔揽权纲。社稷自底于泰盘之安矣。士奇等虑不及此。但恐圣体易倦。不请视朝。不劝御讲。伈倪玩愒。漫若无事。竟使阉竖窃柄。百僚束手。祖宗之业。日以颠覆而不悟。是可谓国有人乎。○宦者王振擅作威福。太后召之大责。将赐死。 上及诸大臣皆跪为之请。遂宥之。按国之杀一宦官。是胡大事。而君臣齐跪勤请不已。不待王振之专权。而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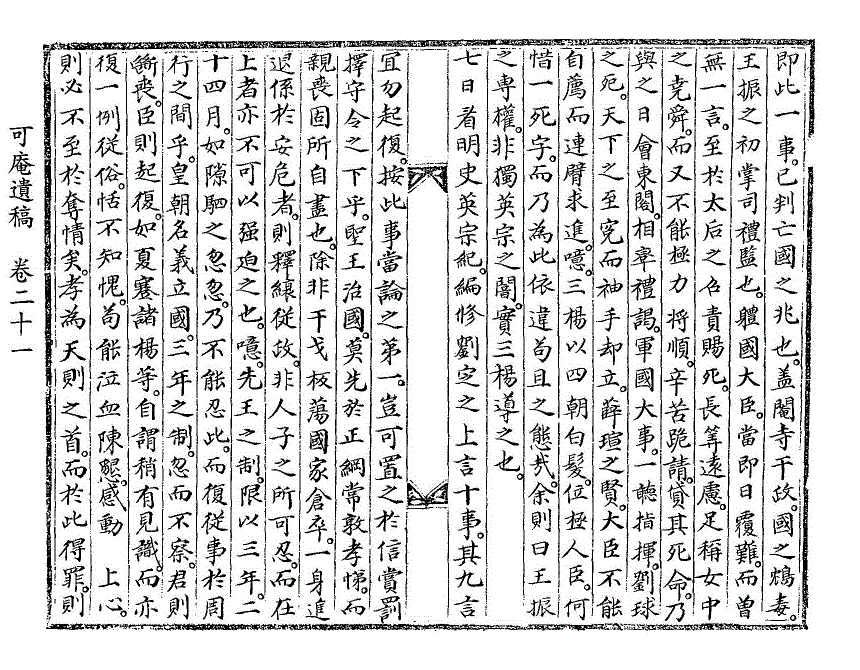 即此一事。已判亡国之兆也。盖阉寺干政。国之鸩毒。王振之初掌司礼监也。体国大臣。当即日覆难。而曾无一言。至于太后之召责赐死。长算远虑。足称女中之尧舜。而又不能极力将顺。辛苦跪请。贷其死命。乃与之日会东阁。相率礼谒。军国大事。一听指挥。刘球之死。天下之至冤而袖手却立。薛瑄之贤。大臣不能自荐而连臂求进。噫。三杨以四朝白发。位极人臣。何惜一死字。而乃为此依违苟且之态哉。余则曰王振之专权。非独英宗之闇。实三杨导之也。
即此一事。已判亡国之兆也。盖阉寺干政。国之鸩毒。王振之初掌司礼监也。体国大臣。当即日覆难。而曾无一言。至于太后之召责赐死。长算远虑。足称女中之尧舜。而又不能极力将顺。辛苦跪请。贷其死命。乃与之日会东阁。相率礼谒。军国大事。一听指挥。刘球之死。天下之至冤而袖手却立。薛瑄之贤。大臣不能自荐而连臂求进。噫。三杨以四朝白发。位极人臣。何惜一死字。而乃为此依违苟且之态哉。余则曰王振之专权。非独英宗之闇。实三杨导之也。七日看明史英宗纪。编修刘定之上言十事。其九言宜勿起复。按此事当论之第一。岂可置之于信赏罚择守令之下乎。圣王治国。莫先于正纲常敦孝悌。而亲丧固所自尽也。除非干戈板荡国家仓卒。一身进退系于安危者。则释缞从政。非人子之所可忍。而在上者亦不可以强迫之也。噫。先王之制。限以三年。二十四月。如隙驷之匆匆。乃不能忍此。而复从事于周行之间乎。皇朝名义立国。三年之制。忽而不察。君则断丧。臣则起复。如夏蹇诸杨等。自谓稍有见识。而亦复一例从俗。恬不知愧。苟能泣血陈恳。感动 上心。则必不至于夺情矣。孝为天则之首。而于此得罪。则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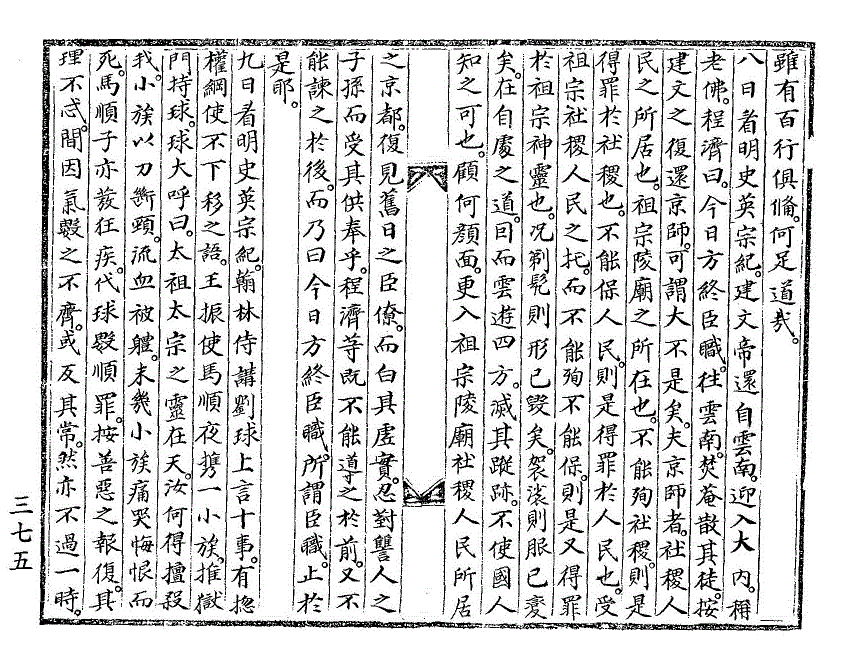 虽有百行俱备。何足道哉。
虽有百行俱备。何足道哉。八日看明史英宗纪。建文帝还自云南。迎入大内。称老佛。程济曰。今日方终臣职。往云南。焚庵散其徒。按建文之复还京师。可谓大不是矣。夫京师者。社稷人民之所居也。祖宗陵庙之所在也。不能殉社稷。则是得罪于社稷也。不能保人民。则是得罪于人民也。受祖宗社稷人民之托。而不能殉不能保。则是又得罪于祖宗神灵也。况剃髡则形已毁矣。袈裟则服已变矣。在自处之道。因而云游四方。灭其踪迹。不使国人知之可也。顾何颜面。更入祖宗陵庙社稷人民所居之京都。复见旧日之臣僚。而白其虚实。忍对雠人之子孙而受其供奉乎。程济等既不能导之于前。又不能谏之于后。而乃曰今日方终臣职。所谓臣职。止于是耶。
九日看明史英宗纪。翰林侍讲刘球上言十事。有揔权纲使不下移之语。王振使马顺夜携一小族。推狱门持球。球大呼曰。太祖太宗之灵在天。汝何得擅杀我。小族以刀断颈。流血被体。未几小族痛哭悔恨而死。马顺子亦发狂疾。代球数顺罪。按善恶之报复。其理不忒。间因气数之不齐。或反其常。然亦不过一时。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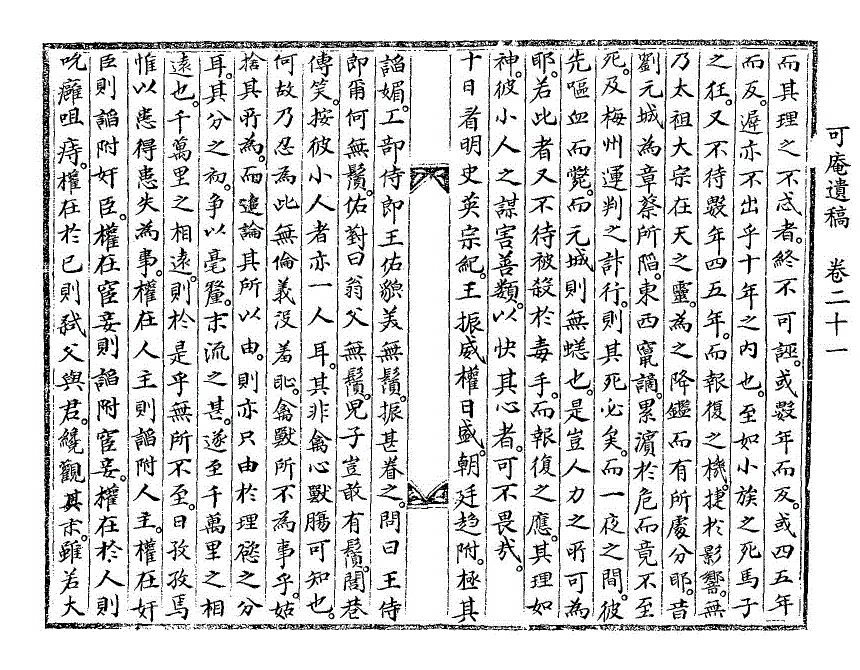 而其理之不忒者。终不可诬。或数年而反。或四五年而反。迟亦不出乎十年之内也。至如小族之死马子之狂。又不待数年四五年。而报复之机。捷于影响。无乃太祖大宗在天之灵。为之降鉴而有所处分耶。昔刘元城为章蔡所陷。东西窜谪。累滨于危而竟不至死。及梅州运判之计行。则其死必矣。而一夜之间。彼先呕血而毙。而元城则无𧏮也。是岂人力之所可为耶。若此者又不待被杀于毒手。而报复之应。其理如神。彼小人之谋害善类。以快其心者。可不畏哉。
而其理之不忒者。终不可诬。或数年而反。或四五年而反。迟亦不出乎十年之内也。至如小族之死马子之狂。又不待数年四五年。而报复之机。捷于影响。无乃太祖大宗在天之灵。为之降鉴而有所处分耶。昔刘元城为章蔡所陷。东西窜谪。累滨于危而竟不至死。及梅州运判之计行。则其死必矣。而一夜之间。彼先呕血而毙。而元城则无𧏮也。是岂人力之所可为耶。若此者又不待被杀于毒手。而报复之应。其理如神。彼小人之谋害善类。以快其心者。可不畏哉。十日看明史英宗纪。王振威权日盛。朝廷趋附。极其谄媚。工部侍郎王佑貌美无须。振甚眷之。问曰王侍郎尔何无须。佑对曰翁父无须。儿子岂敢有须。闾巷传笑。按彼小人者亦一人耳。其非禽心兽肠可知也。何故乃忍为此无伦义没羞耻。禽兽所不为事乎。姑舍其所为。而追论其所以由。则亦只由于理欲之分耳。其分之初。争以毫釐。末流之甚。遂至千万里之相远也。千万里之相远。则于是乎无所不至。日孜孜焉惟以患得患失为事。权在人主则谄附人主。权在奸臣则谄附奸臣。权在宦妾则谄附宦妾。权在于人则吮痈咀痔。权在于己则弑父与君。才观其末。虽若大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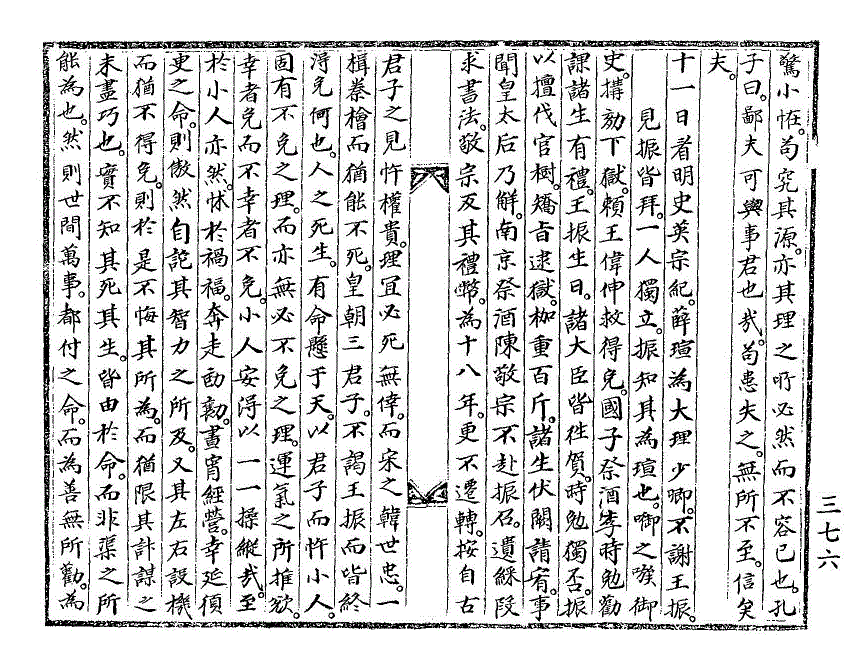 惊小怪。苟究其源。亦其理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信矣夫。
惊小怪。苟究其源。亦其理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信矣夫。十一日看明史英宗纪。薛瑄为大理少卿。不谢王振。▣▣见振皆拜。一人独立。振知其为瑄也。㘅之嗾御史。搆劾下狱。赖王伟伸救得免。国子祭酒李时勉劝课诸生有礼。王振生日。诸大臣皆往贺。时勉独否。振以擅伐官树。矫旨逮狱。枷重百斤。诸生伏阙请宥。事闻皇太后乃解。南京祭酒陈敬宗不赴振召。遗䌽段求书法。敬宗反其礼币。为十八年。更不迁转。按自古君子之见忤权贵。理宜必死无倖。而宋之韩世忠。一楫秦桧而犹能不死。皇朝三君子。不谒王振而皆终得免何也。人之死生。有命悬于天。以君子而忤小人。固有不免之理。而亦无必不免之理。运气之所推敚。幸者免而不幸者不免。小人安得以一一操纵哉。至于小人亦然。怵于祸福。奔走劻勷。昼宵经营。幸延须臾之命。则傲然自詑其智力之所及。又其左右设机而犹不得免。则于是不悔其所为。而犹限其计谋之未尽巧也。实不知其死其生。皆由于命。而非渠之所能为也。然则世间万事。都付之命。而为善无所劝。为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7H 页
 恶无所惩欤。曰福善祸淫。乃理之当然耳。君子之生。小人之死。据其当然而谓之理也。不亦可乎。君子之死。小人之生。据其反常而谓之命也。不亦可乎。故君子先理而后命。小人不循理而亦不信命。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况反常者行乎一时。当然者亘于万世。与其不顾万世之当然。以倖一时之反常。孰若姑与一时之反常。以取万世之当然乎。岳武穆赐死狱中而照心汗青。秦桧得保天年而遗臭无穷。为岳武穆可乎。为秦桧可乎。利害之皎然。不啻如黑白。虽小人亦必易见易知。而终不免出乎此而陷乎彼。吁可哀哉。
恶无所惩欤。曰福善祸淫。乃理之当然耳。君子之生。小人之死。据其当然而谓之理也。不亦可乎。君子之死。小人之生。据其反常而谓之命也。不亦可乎。故君子先理而后命。小人不循理而亦不信命。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况反常者行乎一时。当然者亘于万世。与其不顾万世之当然。以倖一时之反常。孰若姑与一时之反常。以取万世之当然乎。岳武穆赐死狱中而照心汗青。秦桧得保天年而遗臭无穷。为岳武穆可乎。为秦桧可乎。利害之皎然。不啻如黑白。虽小人亦必易见易知。而终不免出乎此而陷乎彼。吁可哀哉。十二日看明史英宗纪。陕西御史陈镒忠厚端谨。用法宽平。人皆爱之。呼为胡子爷。有疾者不事医药。而舁镒轿辄差。一出行台。人争舁之。按不事医药。而舁轿瘳疾。是无于理之理也。若以为神化所暨。民物咸若。一气冲和。疹孽自销。则虽以尧舜孔子之圣。未信其必如是也。陈公之治陕。善则善矣。而论其极处。亦不过为龚黄之流。何足以与于此哉。是特一时偶然之事。抑愚氓趋风。以不然为然者欤。浮诞之说。史氏录之误矣。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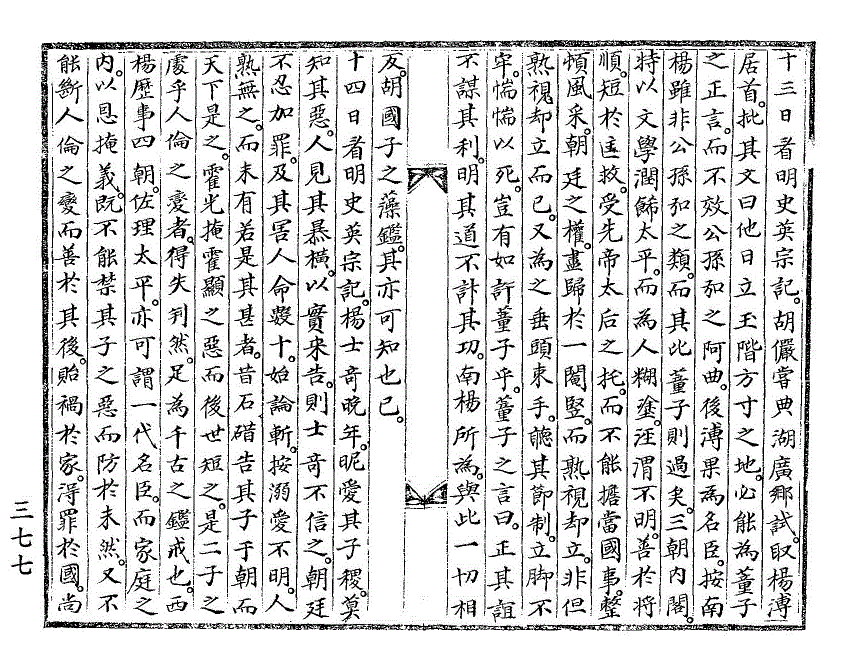 十三日看明史英宗记。胡俨尝典湖广乡试。取杨溥居首。批其文曰他日立玉阶方寸之地。必能为蕫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孙弘之阿曲。后溥果为名臣。按南杨虽非公孙弘之类。而其比蕫子则过矣。三朝内阁。特以文学润饰太平。而为人糊涂。泾渭不明。善于将顺。短于匡救。受先帝太后之托。而不能担当国事。整顿风采。朝廷之权。尽归于一阉竖。而熟视却立。非但熟视却立而已。又为之垂头束手。听其节制。立脚不牢。惴惴以死。岂有如许蕫子乎。蕫子之言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南杨所为。与此一切相反。胡国子之藻鉴。其亦可知也已。
十三日看明史英宗记。胡俨尝典湖广乡试。取杨溥居首。批其文曰他日立玉阶方寸之地。必能为蕫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孙弘之阿曲。后溥果为名臣。按南杨虽非公孙弘之类。而其比蕫子则过矣。三朝内阁。特以文学润饰太平。而为人糊涂。泾渭不明。善于将顺。短于匡救。受先帝太后之托。而不能担当国事。整顿风采。朝廷之权。尽归于一阉竖。而熟视却立。非但熟视却立而已。又为之垂头束手。听其节制。立脚不牢。惴惴以死。岂有如许蕫子乎。蕫子之言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南杨所为。与此一切相反。胡国子之藻鉴。其亦可知也已。十四日看明史英宗记。杨士奇晚年。昵爱其子稷。莫知其恶。人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则士奇不信之。朝廷不忍加罪。及其害人命数十。始论斩。按溺爱不明。人熟无之。而未有若是其甚者。昔石碏告其子于朝而天下是之。霍光掩霍显之恶而后世短之。是二子之处乎人伦之变者。得失判然。足为千古之鉴戒也。西杨历事四朝。佐理太平。亦可谓一代名臣。而家庭之内。以恩掩义。既不能禁其子之恶而防于未然。又不能断人伦之变而善于其后。贻祸于家。得罪于国。尚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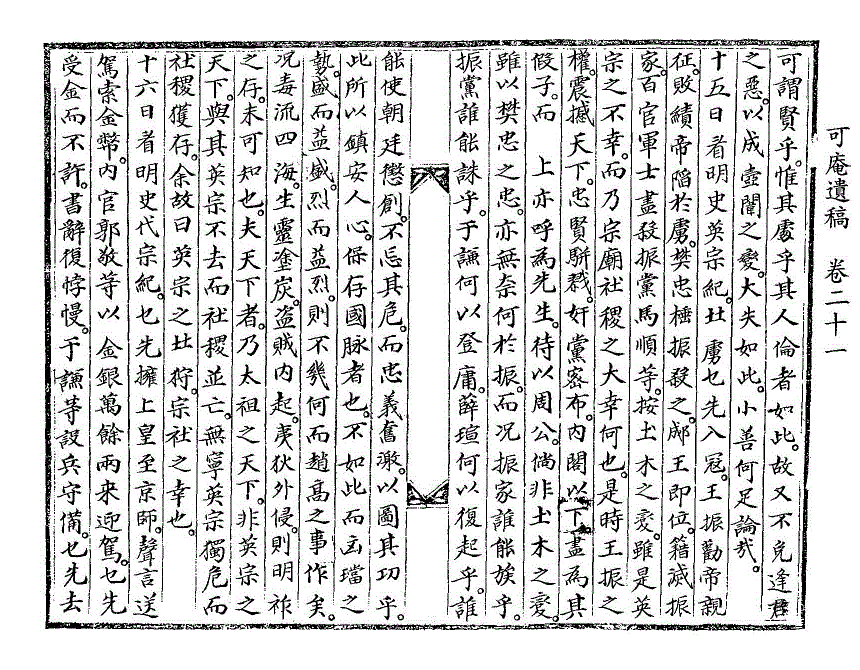 可谓贤乎。惟其处乎其人伦者如此。故又不免逢君之恶。以成壸闱之变。大失如此。小善何足论哉。
可谓贤乎。惟其处乎其人伦者如此。故又不免逢君之恶。以成壸闱之变。大失如此。小善何足论哉。十五日看明史英宗纪。北虏乜先入寇。王振劝帝亲征。败绩帝陷于虏。樊忠棰振杀之。郕王即位。籍灭振家。百官军士尽杀振党马顺等。按土木之变。虽是英宗之不幸。而乃宗庙社稷之大幸何也。是时王振之权。震撼天下。忠贤骈戮。奸党密布。内阁以下。尽为其假子。而 上亦呼为先生。待以周公。倘非土木之变。虽以樊忠之忠。亦无奈何于振。而况振家谁能族乎。振党谁能诛乎。于谦何以登庸。薛瑄何以复起乎。谁能使朝廷惩创。不忘其危。而忠义奋激。以图其功乎。此所以镇安人心。保存国脉者也。不如此而凶珰之势。盛而益盛。烈而益烈。则不几何而赵高之事作矣。况毒流四海。生灵涂炭。盗贼内起。夷狄外侵。则明祚之存。未可知也。夫天下者。乃太祖之天下。非英宗之天下。与其英宗不去而社稷并亡。无宁英宗独危而社稷获存。余故曰英宗之北狩。宗社之幸也。
十六日看明史代宗纪。乜先拥上皇至京师。声言送驾索金币。内官郭敬等以金银万馀两来迎驾。乜先受金而不许。书辞复悖慢。于谦等设兵守备。乜先去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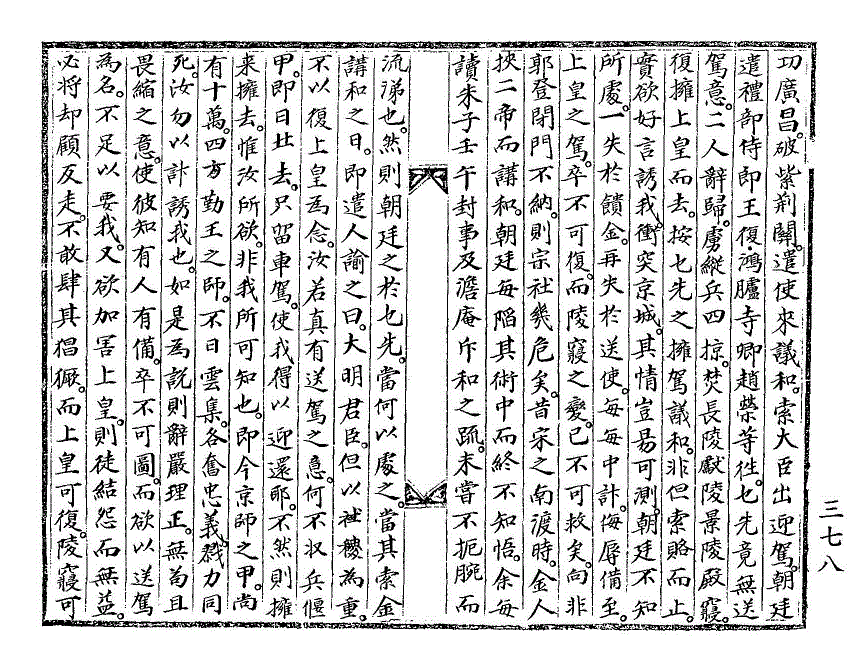 功广昌。破紫荆关。遣使来议和。索大臣出迎驾。朝廷遣礼部侍郎王复,鸿胪寺卿赵荣等往。乜先竟无送驾意。二人辞归。虏纵兵四掠。焚长陵献陵景陵殿寝。复拥上皇而去。按乜先之拥驾议和。非但索赂而止。实欲好言诱我。冲突京城。其情岂易可测。朝廷不知所处。一失于馈金。再失于送使。每每中计。侮辱备至。上皇之驾。卒不可复。而陵寝之变。已不可救矣。向非郭登闭门不纳。则宗社几危矣。昔宋之南渡时。金人挟二帝而讲和。朝廷每陷其术中而终不知悟。余每读朱子壬午封事及澹庵斥和之疏。未尝不扼腕而流涕也。然则朝廷之于乜先。当何以处之。当其索金讲和之日。即遣人谕之曰。大明君臣。但以社稷为重。不以复上皇为念。汝若真有送驾之意。何不收兵偃甲。即日北去。只留车驾。使我得以迎还耶。不然则拥来拥去。惟汝所欲。非我所可知也。即今京师之甲。尚有十万。四方勤王之师。不日云集。各奋忠义。戮力同死。汝勿以计诱我也。如是为说则辞严理正。无苟且畏缩之意。使彼知有人有备。卒不可图。而欲以送驾为名。不足以要我。又欲加害上皇。则徒结怨而无益。必将却顾反走。不敢肆其猖獗。而上皇可复。陵寝可
功广昌。破紫荆关。遣使来议和。索大臣出迎驾。朝廷遣礼部侍郎王复,鸿胪寺卿赵荣等往。乜先竟无送驾意。二人辞归。虏纵兵四掠。焚长陵献陵景陵殿寝。复拥上皇而去。按乜先之拥驾议和。非但索赂而止。实欲好言诱我。冲突京城。其情岂易可测。朝廷不知所处。一失于馈金。再失于送使。每每中计。侮辱备至。上皇之驾。卒不可复。而陵寝之变。已不可救矣。向非郭登闭门不纳。则宗社几危矣。昔宋之南渡时。金人挟二帝而讲和。朝廷每陷其术中而终不知悟。余每读朱子壬午封事及澹庵斥和之疏。未尝不扼腕而流涕也。然则朝廷之于乜先。当何以处之。当其索金讲和之日。即遣人谕之曰。大明君臣。但以社稷为重。不以复上皇为念。汝若真有送驾之意。何不收兵偃甲。即日北去。只留车驾。使我得以迎还耶。不然则拥来拥去。惟汝所欲。非我所可知也。即今京师之甲。尚有十万。四方勤王之师。不日云集。各奋忠义。戮力同死。汝勿以计诱我也。如是为说则辞严理正。无苟且畏缩之意。使彼知有人有备。卒不可图。而欲以送驾为名。不足以要我。又欲加害上皇。则徒结怨而无益。必将却顾反走。不敢肆其猖獗。而上皇可复。陵寝可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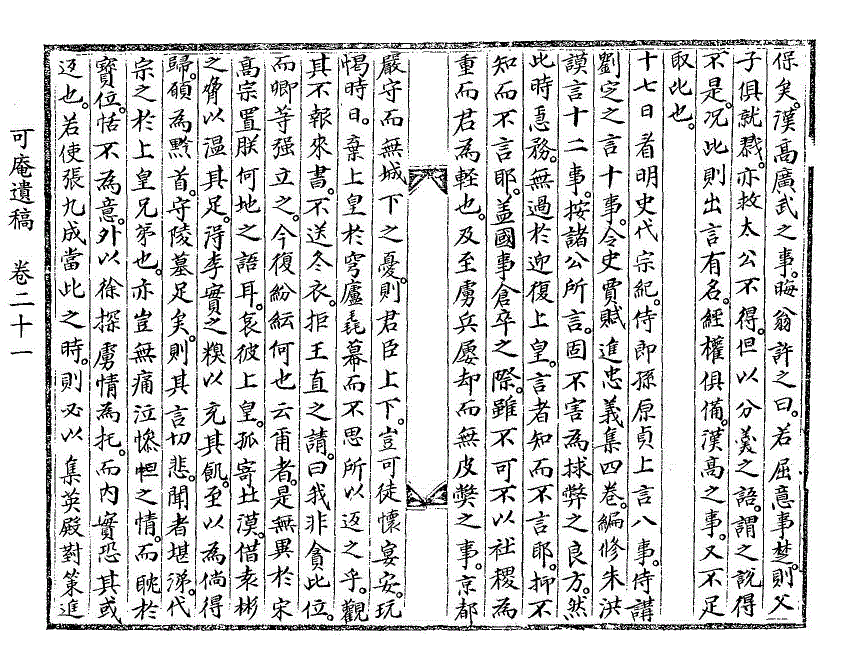 保矣。汉高广武之事。晦翁许之曰。若屈意事楚。则父子俱就戮。亦救太公不得。但以分羹之语。谓之说得不是。况此则出言有名。经权俱备。汉高之事。又不足取比也。
保矣。汉高广武之事。晦翁许之曰。若屈意事楚。则父子俱就戮。亦救太公不得。但以分羹之语。谓之说得不是。况此则出言有名。经权俱备。汉高之事。又不足取比也。十七日看明史代宗纪。侍郎孙原贞上言八事。侍讲刘定之言十事。令史贾赋进忠义集四卷。编修朱洪谟言十二事。按诸公所言。固不害为救弊之良方。然此时急务。无过于迎复上皇。言者知而不言耶。抑不知而不言耶。盖国事仓卒之际。虽不可不以社稷为重而君为轻也。及至虏兵屡却而无皮弊之事。京都严守而无城下之忧。则君臣上下。岂可徒怀宴安。玩愒时日。弃上皇于穹庐毳幕而不思所以返之乎。观其不报来书。不送冬衣。拒王直之请。曰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立之。今复纷纭何也云尔者。是无异于宋高宗置朕何地之语耳。哀彼上皇。孤寄北漠。借袁彬之胁以温其足。得李实之糗以充其饥。至以为倘得归。愿为黔首。守陵墓足矣。则其言切悲。闻者堪涕。代宗之于上皇兄弟也。亦岂无痛泣惨怛之情。而耽于宝位。恬不为意。外以徐探虏情为托。而内实恐其或返也。若使张九成当此之时。则必以集英殿对策进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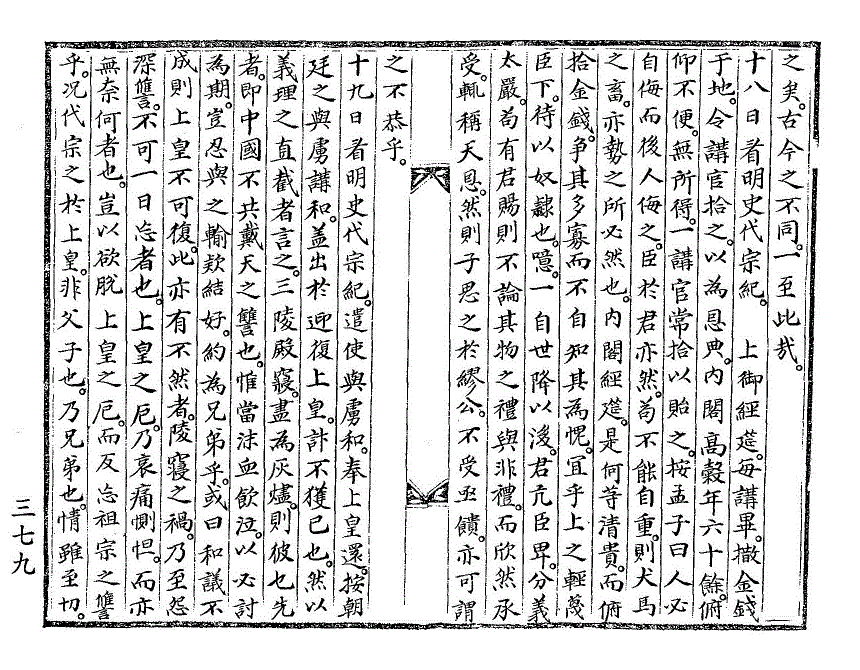 之矣。古今之不同。一至此哉。
之矣。古今之不同。一至此哉。十八日看明史代宗纪。 上御经筵。每讲毕。撒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内阁高谷年六十馀。俯仰不便。无所得。一讲官常拾以贻之。按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臣于君亦然。苟不能自重。则犬马之畜。亦势之所必然也。内阁经筵。是何等清贵。而俯拾金钱。争其多寡而不自知其为愧。宜乎上之轻蔑臣下。待以奴隶也。噫。一自世降以后。君亢臣卑。分义太严。苟有君赐则不论其物之礼与非礼。而欣然承受。辄称天恩。然则子思之于缪公。不受亟馈。亦可谓之不恭乎。
十九日看明史代宗纪。遣使与虏和。奉上皇还。按朝廷之与虏讲和。盖出于迎复上皇。计不获已也。然以义理之直截者言之。三陵殿寝。尽为灰烬。则彼乜先者。即中国不共戴天之雠也。惟当沫血饮泣。以必讨为期。岂忍与之输款结好。约为兄弟乎。或曰和议不成则上皇不可复。此亦有不然者。陵寝之祸。乃至怨深雠。不可一日忘者也。上皇之厄。乃哀痛恻怛。而亦无奈何者也。岂以欲脱上皇之厄。而反忘祖宗之雠乎。况代宗之于上皇。非父子也。乃兄弟也。情虽至切。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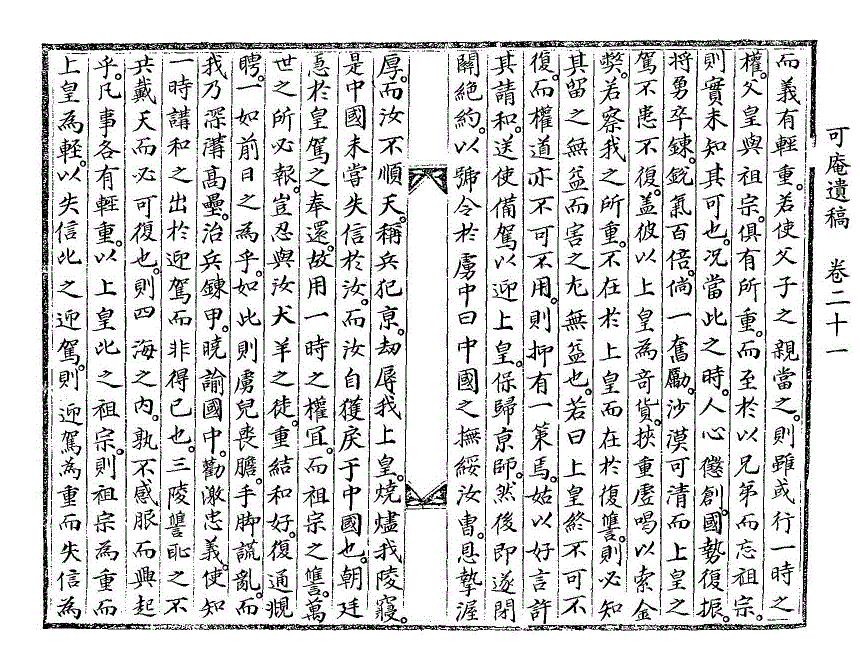 而义有轻重。若使父子之亲当之。则虽或行一时之权。父皇与祖宗。俱有所重。而至于以兄弟而忘祖宗。则实未知其可也。况当此之时。人心惩创。国势复振。将勇卒鍊。锐气百倍。倘一奋励。沙漠可清而上皇之驾不患不复。盖彼以上皇为奇货。挟重虚喝以索金弊。若察我之所重。不在于上皇而在于复雠。则必知其留之无益而害之尤无益也。若曰上皇终不可不复。而权道亦不可不用。则抑有一策焉。姑以好言许其请和。送使备驾以迎上皇。保归京师。然后即遂闭关绝约。以号令于虏中曰中国之抚绥汝曹。恩挚渥厚。而汝不顺天。称兵犯京。劫辱我上皇。烧烬我陵寝。是中国未尝失信于汝。而汝自获戾于中国也。朝廷急于皇驾之奉还。故用一时之权宜。而祖宗之雠。万世之所必报。岂忍与汝犬羊之徒。重结和好。复通覜聘。一如前日之为乎。如此则虏儿丧胆。手脚谎乱。而我乃深沟高垒。治兵鍊甲。晓谕国中。劝激忠义。使知一时讲和之出于迎驾而非得已也。三陵雠耻之不共戴天而必可复也。则四海之内。孰不感服而兴起乎。凡事各有轻重。以上皇比之祖宗。则祖宗为重而上皇为轻。以失信比之迎驾。则迎驾为重而失信为
而义有轻重。若使父子之亲当之。则虽或行一时之权。父皇与祖宗。俱有所重。而至于以兄弟而忘祖宗。则实未知其可也。况当此之时。人心惩创。国势复振。将勇卒鍊。锐气百倍。倘一奋励。沙漠可清而上皇之驾不患不复。盖彼以上皇为奇货。挟重虚喝以索金弊。若察我之所重。不在于上皇而在于复雠。则必知其留之无益而害之尤无益也。若曰上皇终不可不复。而权道亦不可不用。则抑有一策焉。姑以好言许其请和。送使备驾以迎上皇。保归京师。然后即遂闭关绝约。以号令于虏中曰中国之抚绥汝曹。恩挚渥厚。而汝不顺天。称兵犯京。劫辱我上皇。烧烬我陵寝。是中国未尝失信于汝。而汝自获戾于中国也。朝廷急于皇驾之奉还。故用一时之权宜。而祖宗之雠。万世之所必报。岂忍与汝犬羊之徒。重结和好。复通覜聘。一如前日之为乎。如此则虏儿丧胆。手脚谎乱。而我乃深沟高垒。治兵鍊甲。晓谕国中。劝激忠义。使知一时讲和之出于迎驾而非得已也。三陵雠耻之不共戴天而必可复也。则四海之内。孰不感服而兴起乎。凡事各有轻重。以上皇比之祖宗。则祖宗为重而上皇为轻。以失信比之迎驾。则迎驾为重而失信为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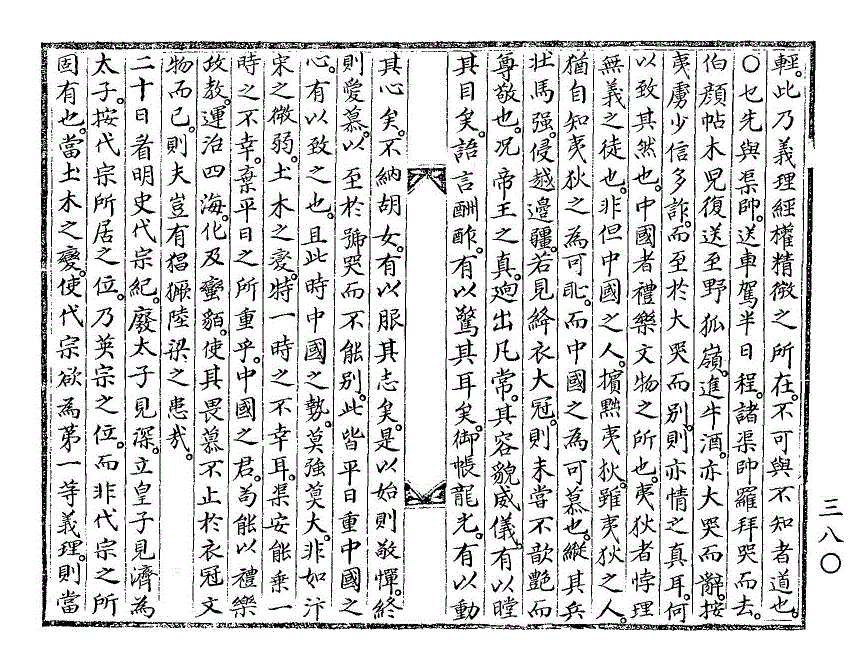 轻。此乃义理经权精微之所在。不可与不知者道也。○乜先与渠帅。送车驾半日程。诸渠帅罗拜哭而去。伯颜帖木儿复送至野狐岭。进牛酒。亦大哭而辞。按夷虏少信多诈。而至于大哭而别。则亦情之真耳。何以致其然也。中国者礼乐文物之所也。夷狄者悖理无义之徒也。非但中国之人。摈黜夷狄。虽夷狄之人。犹自知夷狄之为可耻。而中国之为可慕也。纵其兵壮马强。侵越边彊。若见绛衣大冠。则未尝不歆艳而尊敬也。况帝王之真。迥出凡常。其容貌威仪。有以瞠其目矣。语言酬酢。有以惊其耳矣。御帐龙光。有以动其心矣。不纳胡女。有以服其志矣。是以始则敬惮。终则爱慕。以至于号哭而不能别。此皆平日重中国之心。有以致之也。且此时中国之势。莫强莫大。非如汴宋之微弱。土木之变。特一时之不幸耳。渠安能乘一时之不幸。弃平日之所重乎。中国之君。苟能以礼乐政教。运治四海。化及蛮貊。使其畏慕不止于衣冠文物而已。则夫岂有猖獗陆梁之患哉。
轻。此乃义理经权精微之所在。不可与不知者道也。○乜先与渠帅。送车驾半日程。诸渠帅罗拜哭而去。伯颜帖木儿复送至野狐岭。进牛酒。亦大哭而辞。按夷虏少信多诈。而至于大哭而别。则亦情之真耳。何以致其然也。中国者礼乐文物之所也。夷狄者悖理无义之徒也。非但中国之人。摈黜夷狄。虽夷狄之人。犹自知夷狄之为可耻。而中国之为可慕也。纵其兵壮马强。侵越边彊。若见绛衣大冠。则未尝不歆艳而尊敬也。况帝王之真。迥出凡常。其容貌威仪。有以瞠其目矣。语言酬酢。有以惊其耳矣。御帐龙光。有以动其心矣。不纳胡女。有以服其志矣。是以始则敬惮。终则爱慕。以至于号哭而不能别。此皆平日重中国之心。有以致之也。且此时中国之势。莫强莫大。非如汴宋之微弱。土木之变。特一时之不幸耳。渠安能乘一时之不幸。弃平日之所重乎。中国之君。苟能以礼乐政教。运治四海。化及蛮貊。使其畏慕不止于衣冠文物而已。则夫岂有猖獗陆梁之患哉。二十日看明史代宗纪。废太子见深。立皇子见济为太子。按代宗所居之位。乃英宗之位。而非代宗之所固有也。当土木之变。使代宗欲为第一等义理。则当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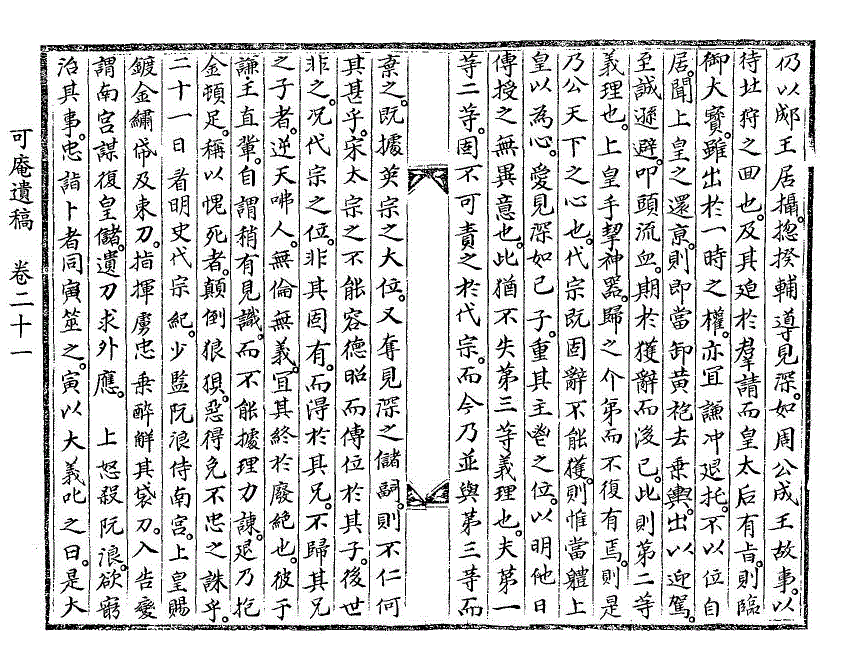 仍以郕王居摄。揔揆辅导见深。如周公成王故事。以待北狩之回也。及其迫于群请而皇太后有旨。则临御大宝。虽出于一时之权。亦宜谦冲退托。不以位自居。闻上皇之还京。则即当卸黄袍去乘舆。出以迎驾。至诚逊避。叩头流血。期于获辞而后已。此则第二等义理也。上皇手挈神器。归之介弟而不复有焉。则是乃公天下之心也。代宗既固辞不能获。则惟当体上皇以为心。爱见深如己子。重其主鬯之位。以明他日传授之无异意也。此犹不失第三等义理也。夫第一等二等。固不可责之于代宗。而今乃并与第三等而弃之。既据英宗之大位。又夺见深之储嗣。则不仁何其甚乎。宋太宗之不能容德昭而传位于其子。后世非之。况代宗之位。非其固有。而得于其兄。不归其兄之子者。逆天咈人。无伦无义。宜其终于废绝也。彼于谦,王直辈。自谓稍有见识。而不能据理力谏。退乃抱金顿足。称以愧死者。颠倒狼狈。恶得免不忠之诛乎。
仍以郕王居摄。揔揆辅导见深。如周公成王故事。以待北狩之回也。及其迫于群请而皇太后有旨。则临御大宝。虽出于一时之权。亦宜谦冲退托。不以位自居。闻上皇之还京。则即当卸黄袍去乘舆。出以迎驾。至诚逊避。叩头流血。期于获辞而后已。此则第二等义理也。上皇手挈神器。归之介弟而不复有焉。则是乃公天下之心也。代宗既固辞不能获。则惟当体上皇以为心。爱见深如己子。重其主鬯之位。以明他日传授之无异意也。此犹不失第三等义理也。夫第一等二等。固不可责之于代宗。而今乃并与第三等而弃之。既据英宗之大位。又夺见深之储嗣。则不仁何其甚乎。宋太宗之不能容德昭而传位于其子。后世非之。况代宗之位。非其固有。而得于其兄。不归其兄之子者。逆天咈人。无伦无义。宜其终于废绝也。彼于谦,王直辈。自谓稍有见识。而不能据理力谏。退乃抱金顿足。称以愧死者。颠倒狼狈。恶得免不忠之诛乎。二十一日看明史代宗纪。少监阮浪侍南宫。上皇赐镀金绣袋及束刀。指挥虏忠乘醉解其袋刀。入告变谓南宫谋复皇储。遗刀求外应。 上怒杀阮浪。欲穷治其事。忠诣卜者同寅筮之。寅以大义叱之曰。是大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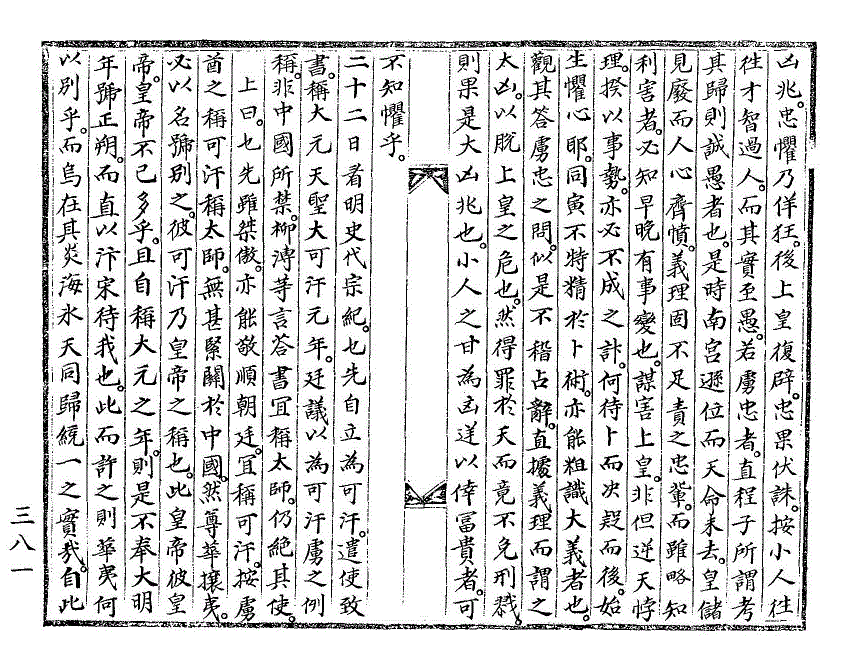 凶兆。忠惧乃佯狂。后上皇复辟。忠果伏诛。按小人往往才智过人。而其实至愚。若虏忠者。直程子所谓考其归则诚愚者也。是时南宫逊位而天命未去。皇储见废而人心齐愤。义理固不足责之忠辈。而虽略知利害者。必知早晚有事变也。谋害上皇。非但逆天悖理。揆以事势。亦必不成之计。何待卜而决疑而后。始生惧心耶。同寅不特精于卜术。亦能粗识大义者也。观其答虏忠之问。似是不稽占辞。直据义理而谓之大凶。以脱上皇之危也。然得罪于天而竟不免刑戮。则果是大凶兆也。小人之甘为凶逆以倖富贵者。可不知惧乎。
凶兆。忠惧乃佯狂。后上皇复辟。忠果伏诛。按小人往往才智过人。而其实至愚。若虏忠者。直程子所谓考其归则诚愚者也。是时南宫逊位而天命未去。皇储见废而人心齐愤。义理固不足责之忠辈。而虽略知利害者。必知早晚有事变也。谋害上皇。非但逆天悖理。揆以事势。亦必不成之计。何待卜而决疑而后。始生惧心耶。同寅不特精于卜术。亦能粗识大义者也。观其答虏忠之问。似是不稽占辞。直据义理而谓之大凶。以脱上皇之危也。然得罪于天而竟不免刑戮。则果是大凶兆也。小人之甘为凶逆以倖富贵者。可不知惧乎。二十二日看明史代宗纪。乜先自立为可汗。遣使致书。称大元天圣大可汗元年。廷议以为可汗虏之例称。非中国所禁。柳溥等言答书宜称太师。仍绝其使。 上曰。乜先虽桀傲。亦能敬顺朝廷。宜称可汗。按虏酋之称可汗称太师。无甚紧关于中国。然尊华攘夷。必以名号别之。彼可汗乃皇帝之称也。此皇帝彼皇帝。皇帝不已多乎。且自称大元之年。则是不奉大明年号正朔。而直以汴宋待我也。此而许之则华夷何以别乎。而乌在其炎海冰天同归统一之实哉。自此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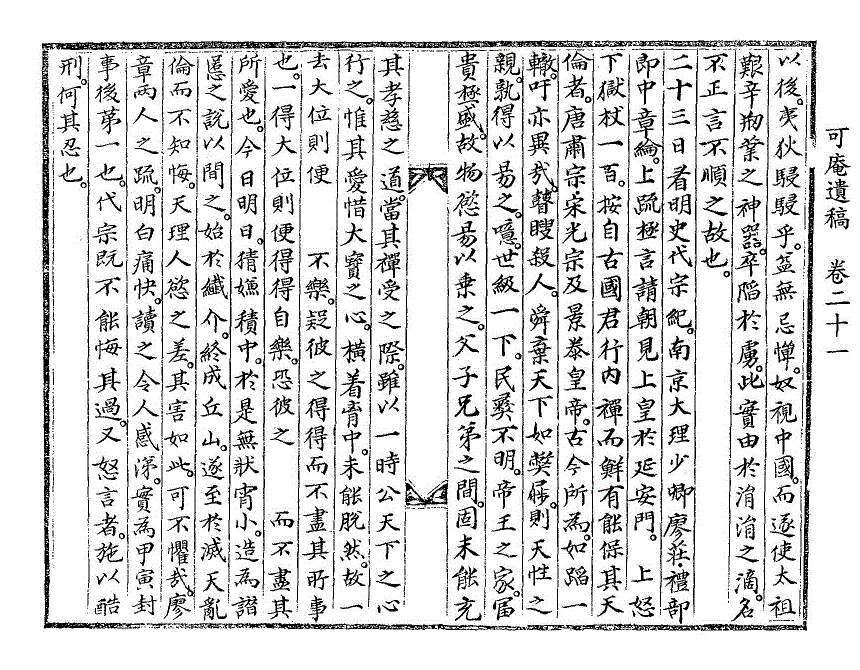 以后。夷狄骎骎乎。益无忌惮。奴视中国。而遂使太祖艰辛刱业之神器。卒陷于虏。此实由于涓涓之滴。名不正言不顺之故也。
以后。夷狄骎骎乎。益无忌惮。奴视中国。而遂使太祖艰辛刱业之神器。卒陷于虏。此实由于涓涓之滴。名不正言不顺之故也。二十三日看明史代宗纪。南京大理少卿廖庄,礼部郎中章纶。上疏极言请朝见上皇于延安门。 上怒下狱杖一百。按自古国君行内禅而鲜有能保其天伦者。唐肃宗,宋光宗及景泰皇帝。古今所为。如蹈一辙。吁亦异哉。瞽瞍杀人。舜弃天下如弊屣。则天性之亲。孰得以易之。噫。世级一下。民彝不明。帝王之家。富贵极盛。故物欲易以乘之。父子兄弟之间。固未能充其孝慈之道。当其禅受之际。虽以一时公天下之心行之。惟其爱惜大宝之心。横着胸中。未能脱然。故一去大位则便▣▣不乐。疑彼之得得而不尽其所事也。一得大位则便得得自乐。恐彼之▣▣而不尽其所爱也。今日明日。猜嫌积中。于是无状宵小。造为谮慝之说以间之。始于纤介。终成丘山。遂至于灭天乱伦而不知悔。天理人欲之差。其害如此。可不惧哉。廖章两人之疏。明白痛快。读之令人感涕。实为甲寅封事后第一也。代宗既不能悔其过。又怒言者。施以酷刑。何其忍也。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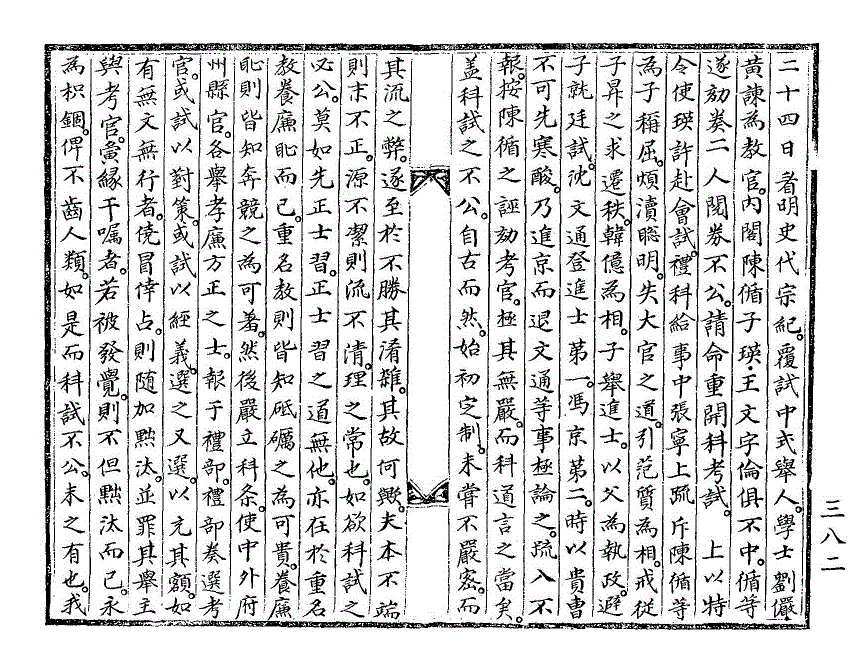 二十四日看明史代宗纪。覆试中式举人。学士刘俨,黄谏为教官。内阁陈循子瑛,王文字伦俱不中。循等遂劾奏二人阅券不公。请命重开科考试。 上以特令使瑛许赴会试。礼科给事中张宁上疏斥陈循等为子称屈。烦渎聪明。失大官之道。引范质为相。戒从子升之求迁秩。韩亿为相。子举进士。以父为执政。避子就廷试。沈文通登进士第一。冯京第二。时以贵曹不可先寒酸。乃进京而退文通等事极论之。疏入不报。按陈循之诬劾考官。极其无严。而科道言之当矣。盖科试之不公。自古而然。始初定制。未尝不严密。而其流之弊。遂至于不胜其淆杂。其故何欤。夫本不端则末不正。源不洁则流不清。理之常也。如欲科试之必公。莫如先正士习。正士习之道无他。亦在于重名教养廉耻而已。重名教则皆知砥砺之为可贵。养廉耻则皆知奔竞之为可羞。然后严立科条。使中外府州县官。各举孝廉方正之士。报于礼部。礼部奏选考官。或试以对策。或试以经义。选之又选。以充其额。如有无文无行者。侥冒倖占。则随加黜汰。并罪其举主与考官。夤缘干嘱者。若被发觉。则不但黜汰而已。永为枳锢。俾不齿人类。如是而科试不公。未之有也。我
二十四日看明史代宗纪。覆试中式举人。学士刘俨,黄谏为教官。内阁陈循子瑛,王文字伦俱不中。循等遂劾奏二人阅券不公。请命重开科考试。 上以特令使瑛许赴会试。礼科给事中张宁上疏斥陈循等为子称屈。烦渎聪明。失大官之道。引范质为相。戒从子升之求迁秩。韩亿为相。子举进士。以父为执政。避子就廷试。沈文通登进士第一。冯京第二。时以贵曹不可先寒酸。乃进京而退文通等事极论之。疏入不报。按陈循之诬劾考官。极其无严。而科道言之当矣。盖科试之不公。自古而然。始初定制。未尝不严密。而其流之弊。遂至于不胜其淆杂。其故何欤。夫本不端则末不正。源不洁则流不清。理之常也。如欲科试之必公。莫如先正士习。正士习之道无他。亦在于重名教养廉耻而已。重名教则皆知砥砺之为可贵。养廉耻则皆知奔竞之为可羞。然后严立科条。使中外府州县官。各举孝廉方正之士。报于礼部。礼部奏选考官。或试以对策。或试以经义。选之又选。以充其额。如有无文无行者。侥冒倖占。则随加黜汰。并罪其举主与考官。夤缘干嘱者。若被发觉。则不但黜汰而已。永为枳锢。俾不齿人类。如是而科试不公。未之有也。我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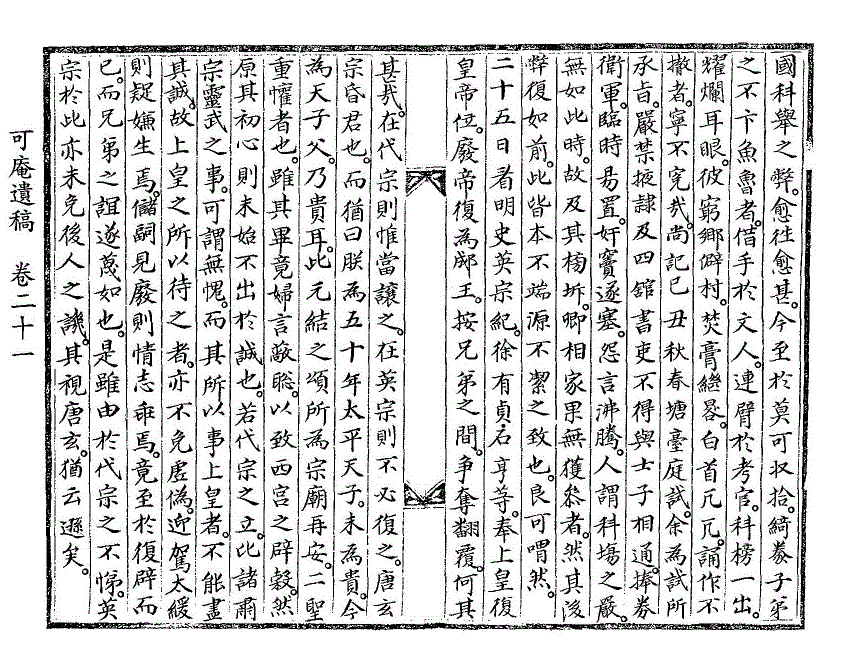 国科举之弊。愈往愈甚。今至于莫可收拾。绮豢子弟之不卞鱼鲁者。借手于文人。连臂于考官。科榜一出。耀烂耳眼。彼穷乡僻村。焚膏继晷。白首兀兀。诵作不撤者。宁不冤哉。尚记己丑秋春塘台庭试。余为试所承旨。严禁掖隶及四馆书吏不得与士子相通。捧券卫军。临时易置。奸窦遂塞。怨言沸腾。人谓科场之严。无如此时。故及其榜坼。卿相家果无获参者。然其后弊复如前。此皆本不端源不洁之致也。良可喟然。
国科举之弊。愈往愈甚。今至于莫可收拾。绮豢子弟之不卞鱼鲁者。借手于文人。连臂于考官。科榜一出。耀烂耳眼。彼穷乡僻村。焚膏继晷。白首兀兀。诵作不撤者。宁不冤哉。尚记己丑秋春塘台庭试。余为试所承旨。严禁掖隶及四馆书吏不得与士子相通。捧券卫军。临时易置。奸窦遂塞。怨言沸腾。人谓科场之严。无如此时。故及其榜坼。卿相家果无获参者。然其后弊复如前。此皆本不端源不洁之致也。良可喟然。二十五日看明史英宗纪。徐有贞,石亨等。奉上皇复皇帝位。废帝复为郕王。按兄弟之间。争夺翻覆。何其甚哉。在代宗则惟当让之。在英宗则不必复之。唐玄宗昏君也。而犹曰朕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此元结之颂所为宗庙再安。二圣重欢者也。虽其毕竟妇言蔽聪。以致西宫之辟谷。然原其初心则未始不出于诚也。若代宗之立。比诸肃宗灵武之事。可谓无愧。而其所以事上皇者。不能尽其诚。故上皇之所以待之者。亦不免虚伪。迎驾太缓则疑嫌生焉。储嗣见废则情志乖焉。竟至于复辟而已。而兄弟之谊遂蔑如也。是虽由于代宗之不悌。英宗于此亦未免后人之讥。其视唐玄。犹云逊矣。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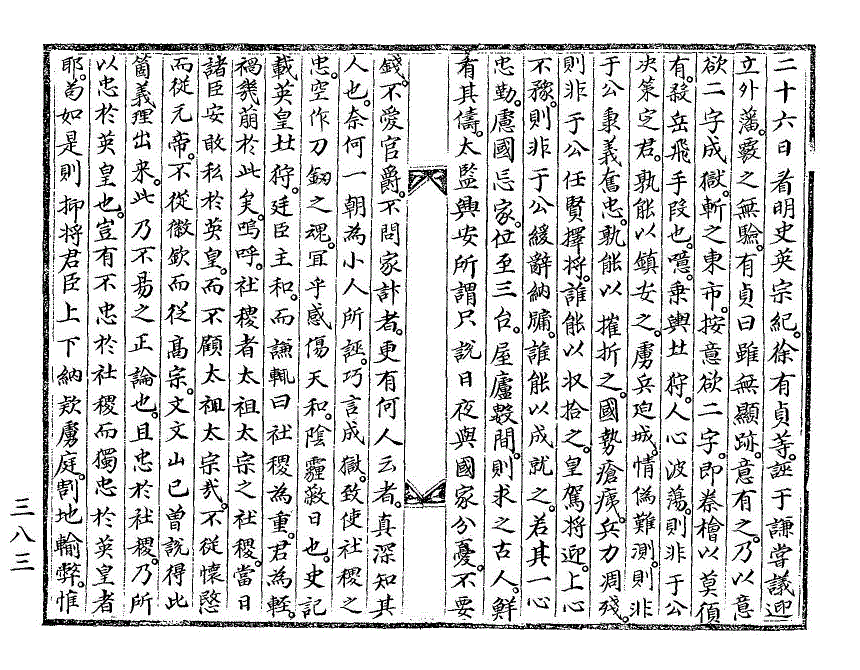 二十六日看明史英宗纪。徐有贞等。诬于谦尝议迎立外藩。覈之无验。有贞曰虽无显迹。意有之。乃以意欲二字成狱。斩之东市。按意欲二字。即秦桧以莫须有。杀岳飞手段也。噫。乘舆北狩。人心波荡。则非于公决策定君。孰能以镇安之。虏兵迫城。情伪难测。则非于公秉义奋忠。孰能以摧折之。国势疮痍。兵力凋残。则非于公任贤择将。谁能以收拾之。皇驾将迎。上心不豫。则非于公缓辞纳牖。谁能以成就之。若其一心忠勤。虑国忘家。位至三台。屋庐数间。则求之古人。鲜有其俦。太监兴安所谓只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者。更有何人云者。真深知其人也。奈何一朝为小人所诬。巧言成狱。致使社稷之忠。空作刀釰之魂。宜乎感伤天和。阴霾蔽日也。史记载英皇北狩。廷臣主和。而谦辄曰社稷为重。君为轻。祸几萌于此矣。呜呼。社稷者太祖太宗之社稷。当日诸臣安敢私于英皇。而不顾太祖太宗哉。不从怀悯而从元帝。不从徽钦而从高宗。文文山已曾说得此个义理出来。此乃不易之正论也。且忠于社稷。乃所以忠于英皇也。岂有不忠于社稷而独忠于英皇者耶。苟如是则抑将君臣上下纳款虏庭。割地输弊。惟
二十六日看明史英宗纪。徐有贞等。诬于谦尝议迎立外藩。覈之无验。有贞曰虽无显迹。意有之。乃以意欲二字成狱。斩之东市。按意欲二字。即秦桧以莫须有。杀岳飞手段也。噫。乘舆北狩。人心波荡。则非于公决策定君。孰能以镇安之。虏兵迫城。情伪难测。则非于公秉义奋忠。孰能以摧折之。国势疮痍。兵力凋残。则非于公任贤择将。谁能以收拾之。皇驾将迎。上心不豫。则非于公缓辞纳牖。谁能以成就之。若其一心忠勤。虑国忘家。位至三台。屋庐数间。则求之古人。鲜有其俦。太监兴安所谓只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者。更有何人云者。真深知其人也。奈何一朝为小人所诬。巧言成狱。致使社稷之忠。空作刀釰之魂。宜乎感伤天和。阴霾蔽日也。史记载英皇北狩。廷臣主和。而谦辄曰社稷为重。君为轻。祸几萌于此矣。呜呼。社稷者太祖太宗之社稷。当日诸臣安敢私于英皇。而不顾太祖太宗哉。不从怀悯而从元帝。不从徽钦而从高宗。文文山已曾说得此个义理出来。此乃不易之正论也。且忠于社稷。乃所以忠于英皇也。岂有不忠于社稷而独忠于英皇者耶。苟如是则抑将君臣上下纳款虏庭。割地输弊。惟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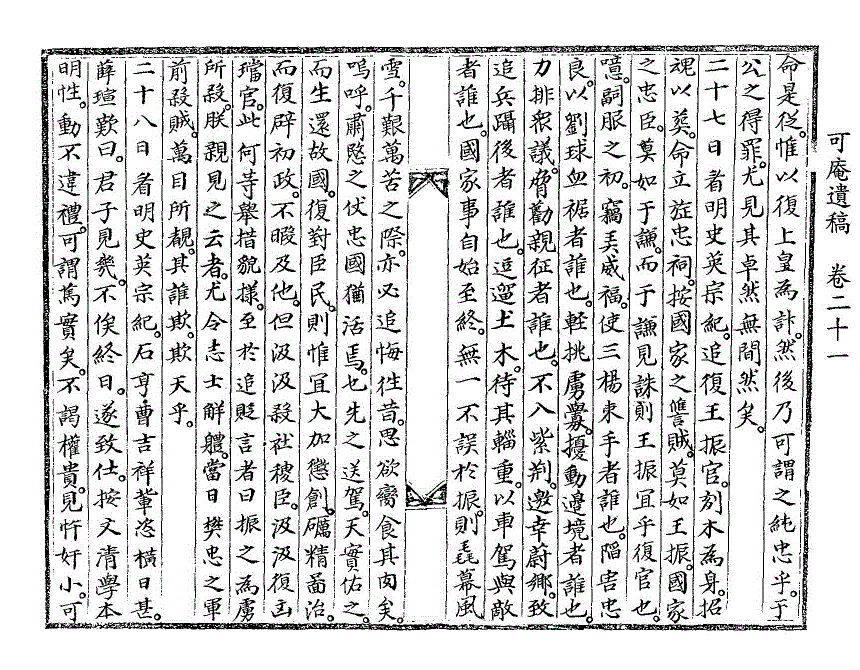 命是从。惟以复上皇为计。然后乃可谓之纯忠乎。于公之得罪。尤见其卓然无间然矣。
命是从。惟以复上皇为计。然后乃可谓之纯忠乎。于公之得罪。尤见其卓然无间然矣。二十七日看明史英宗纪。追复王振官。刻木为身。招魂以葬。命立旌忠祠。按国家之雠贼。莫如王振。国家之忠臣。莫如于谦。而于谦见诛。则王振宜乎复官也。噫。嗣服之初。窃弄威福。使三杨束手者谁也。陷害忠良。以刘球血裾者谁也。轻挑虏衅。扰动边境者谁也。力排众议。胁劝亲征者谁也。不入紫荆。邀幸蔚乡。致追兵蹑后者谁也。逗遛土木。待其辎重。以车驾与敌者谁也。国家事自始至终。无一不误于振。则毳幕风雪。千艰万苦之际。亦必追悔往昔。思欲脔食其肉矣。呜呼。肃悯之仗忠国犹活焉。乜先之送驾。天实佑之。而生还故国。复对臣民。则惟宜大加惩创。砺精啚治。而复辟初政。不暇及他。但汲汲杀社稷臣。汲汲复凶珰官。此何等举措貌㨾。至于追贬言者曰振之为虏所杀。朕亲见之云者。尤令志士解体。当日樊忠之军前杀贼。万目所睹。其谁欺。欺天乎。
二十八日看明史英宗纪。石亨,曹吉祥辈恣横日甚。薛瑄叹曰。君子见几。不俟终日。遂致仕。按文清学本明性。动不违礼。可谓笃实矣。不谒权贵。见忤奸小。可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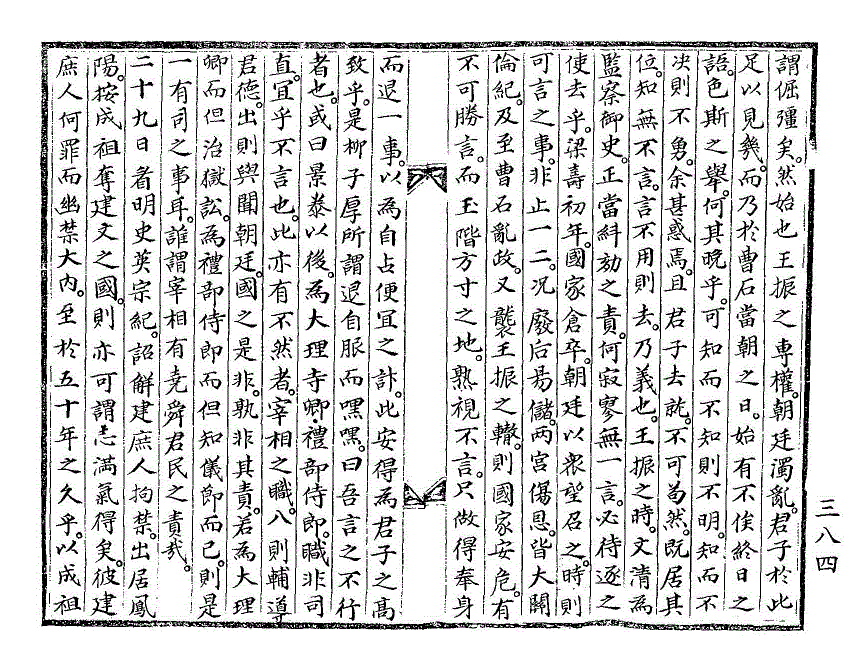 谓倔彊矣。然始也王振之专权。朝廷浊乱。君子于此足以见几。而乃于曹石当朝之日。始有不俟终日之语。色斯之举。何其晚乎。可知而不知则不明。知而不决则不勇。余甚惑焉。且君子去就。不可苟然。既居其位。知无不言。言不用则去。乃义也。王振之时。文清为监察御史。正当纠劾之责。何寂寥无一言。必待逐之使去乎。梁寿初年。国家仓卒。朝廷以众望召之。时则可言之事。非止一二。况废后易储。两宫伤恩。皆大关伦纪。及至曹石乱政。又袭王振之辙。则国家安危。有不可胜言。而玉阶方寸之地。熟视不言。只做得奉身而退一事。以为自占便宜之计。此安得为君子之高致乎。是柳子厚所谓退自服而嘿嘿。曰吾言之不行者也。或曰景泰以后。为大理寺卿,礼部侍郎。职非司直。宜乎不言也。此亦有不然者。宰相之职。入则辅导君德。出则与闻朝廷。国之是非。孰非其责。若为大理卿而但治狱讼。为礼部侍郎而但知仪节而已。则是一有司之事耳。谁谓宰相有尧舜君民之责哉。
谓倔彊矣。然始也王振之专权。朝廷浊乱。君子于此足以见几。而乃于曹石当朝之日。始有不俟终日之语。色斯之举。何其晚乎。可知而不知则不明。知而不决则不勇。余甚惑焉。且君子去就。不可苟然。既居其位。知无不言。言不用则去。乃义也。王振之时。文清为监察御史。正当纠劾之责。何寂寥无一言。必待逐之使去乎。梁寿初年。国家仓卒。朝廷以众望召之。时则可言之事。非止一二。况废后易储。两宫伤恩。皆大关伦纪。及至曹石乱政。又袭王振之辙。则国家安危。有不可胜言。而玉阶方寸之地。熟视不言。只做得奉身而退一事。以为自占便宜之计。此安得为君子之高致乎。是柳子厚所谓退自服而嘿嘿。曰吾言之不行者也。或曰景泰以后。为大理寺卿,礼部侍郎。职非司直。宜乎不言也。此亦有不然者。宰相之职。入则辅导君德。出则与闻朝廷。国之是非。孰非其责。若为大理卿而但治狱讼。为礼部侍郎而但知仪节而已。则是一有司之事耳。谁谓宰相有尧舜君民之责哉。二十九日看明史英宗纪。诏解建庶人拘禁。出居凤阳。按成祖夺建文之国。则亦可谓志满气得矣。彼建庶人何罪而幽禁大内。至于五十年之久乎。以成祖
可庵遗稿卷之二十一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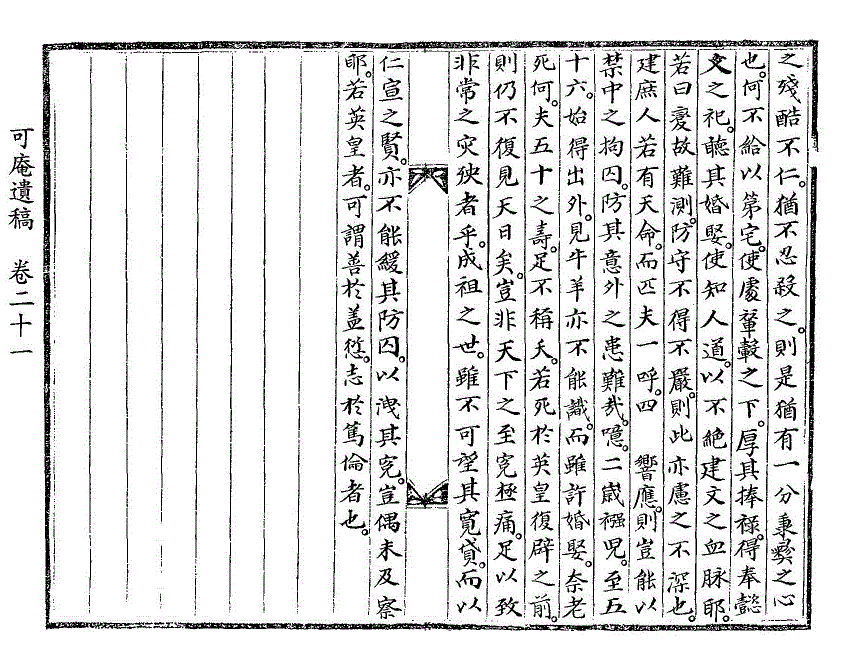 之残酷不仁。犹不忍杀之。则是犹有一分秉彝之心也。何不给以第宅。使处辇毂之下。厚其捧禄。得奉懿文之祀。听其婚娶。使知人道。以不绝建文之血脉耶。若曰变故难测。防守不得不严。则此亦虑之不深也。建庶人若有天命。而匹夫一呼。四▣响应。则岂能以禁中之拘囚。防其意外之患难哉。噫。二岁襁儿。至五十六。始得出外。见牛羊亦不能识。而虽许婚娶。奈老死何。夫五十之寿。足不称夭。若死于英皇复辟之前。则仍不复见天日矣。岂非天下之至冤极痛。足以致非常之灾殃者乎。成祖之世。虽不可望其宽贷。而以仁宣之贤。亦不能缓其防囚。以泄其冤。岂偶未及察耶。若英皇者。可谓善于盖愆。志于笃伦者也。
之残酷不仁。犹不忍杀之。则是犹有一分秉彝之心也。何不给以第宅。使处辇毂之下。厚其捧禄。得奉懿文之祀。听其婚娶。使知人道。以不绝建文之血脉耶。若曰变故难测。防守不得不严。则此亦虑之不深也。建庶人若有天命。而匹夫一呼。四▣响应。则岂能以禁中之拘囚。防其意外之患难哉。噫。二岁襁儿。至五十六。始得出外。见牛羊亦不能识。而虽许婚娶。奈老死何。夫五十之寿。足不称夭。若死于英皇复辟之前。则仍不复见天日矣。岂非天下之至冤极痛。足以致非常之灾殃者乎。成祖之世。虽不可望其宽贷。而以仁宣之贤。亦不能缓其防囚。以泄其冤。岂偶未及察耶。若英皇者。可谓善于盖愆。志于笃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