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x 页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杂著
杂著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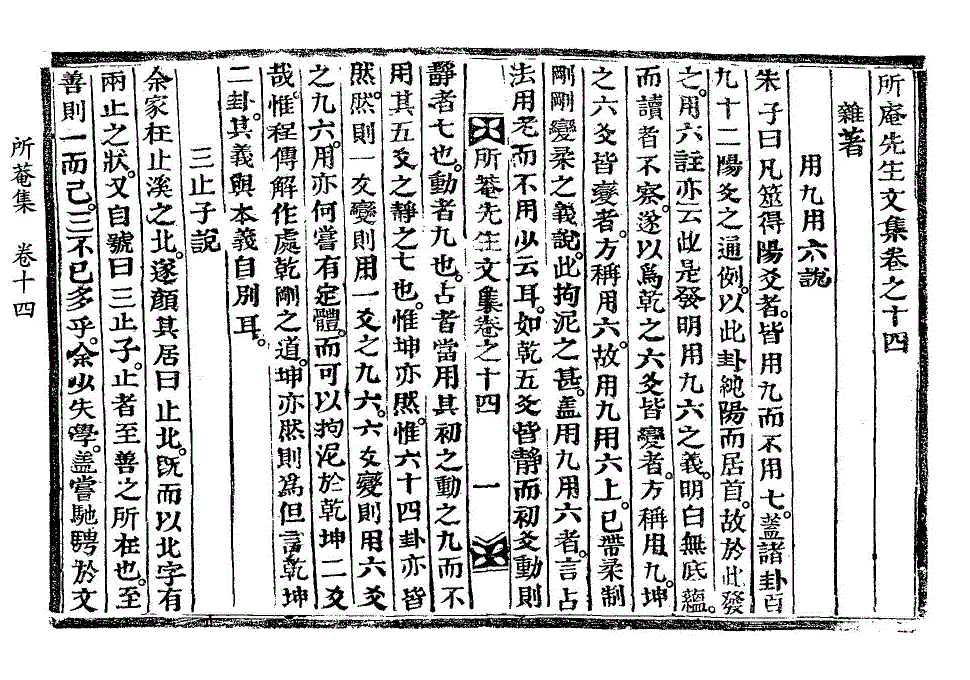 用九用六说
用九用六说朱子曰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用六注亦云此是发明用九六之义。明白无底蕴。而读者不察。遂以为乾之六爻皆变者。方称用九。坤之六爻皆变者。方称用六。故用九用六上。已带柔制刚刚变柔之义说。此拘泥之甚。盖用九用六者。言占法用老而不用少云耳。如乾五爻皆静而初爻动则静者七也。动者九也。占者当用其初之动之九而不用其五爻之静之七也。惟坤亦然。惟六十四卦亦皆然。然则一爻变则用一爻之九六。六爻变则用六爻之九六。用亦何尝有定体。而可以拘泥于乾坤二爻哉。惟程传解作处乾刚之道。坤亦然则为但言乾坤二卦。其义与本义自别耳。
三止子说
余家在止溪之北。遂颜其居曰止北。既而以北字有两止之状。又自号曰三止子。止者至善之所在也。至善则一而已。三不已多乎。余少失学。盖尝驰骋于文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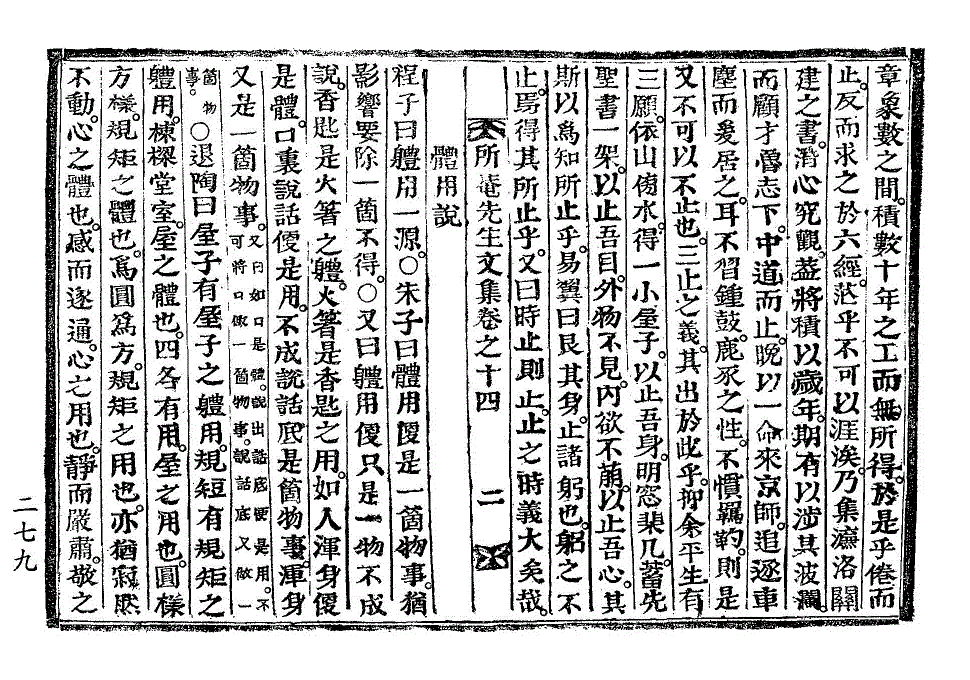 章象数之间。积数十年之工而无所得。于是乎倦而止。反而求之于六经。茫乎不可以涯涘。乃集濂洛关建之书。潜心究观。盖将积以岁年。期有以涉其波澜。而顾才鲁志下。中道而止。晚以一命来京师。追逐车尘而爰居之。耳不习钟鼓。鹿豕之性。不惯羁靮。则是又不可以不止也。三止之义。其出于此乎。抑余平生有三愿。依山傍水。得一小屋子。以止吾身。明窗棐几。蓄先圣书一架。以止吾目。外物不见。内欲不萌。以止吾心。其斯以为知所止乎。易翼曰艮其身。止诸躬也。躬之不止。焉得其所止乎。又曰时止则止。止之时义大矣哉。
章象数之间。积数十年之工而无所得。于是乎倦而止。反而求之于六经。茫乎不可以涯涘。乃集濂洛关建之书。潜心究观。盖将积以岁年。期有以涉其波澜。而顾才鲁志下。中道而止。晚以一命来京师。追逐车尘而爰居之。耳不习钟鼓。鹿豕之性。不惯羁靮。则是又不可以不止也。三止之义。其出于此乎。抑余平生有三愿。依山傍水。得一小屋子。以止吾身。明窗棐几。蓄先圣书一架。以止吾目。外物不见。内欲不萌。以止吾心。其斯以为知所止乎。易翼曰艮其身。止诸躬也。躬之不止。焉得其所止乎。又曰时止则止。止之时义大矣哉。体用说
程子曰体用一源。○朱子曰体用便是一个物事。犹影响要除一个不得。○又曰体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说。香匙是火箸之体。火箸是香匙之用。如人浑身便是体。口里说话便是用。不成说话底是个物事。浑身又是一个物事。(又曰如口是体。说出话底便是用。不可将口做一个物事。说话底又做一个物事。)○退陶曰屋子有屋子之体用。规短有规矩之体用。栋梁堂室。屋之体也。四各有用。屋之用也。圆样方样。规矩之体也。为圆为方。规矩之用也。亦犹寂然不动。心之体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静而严肃。敬之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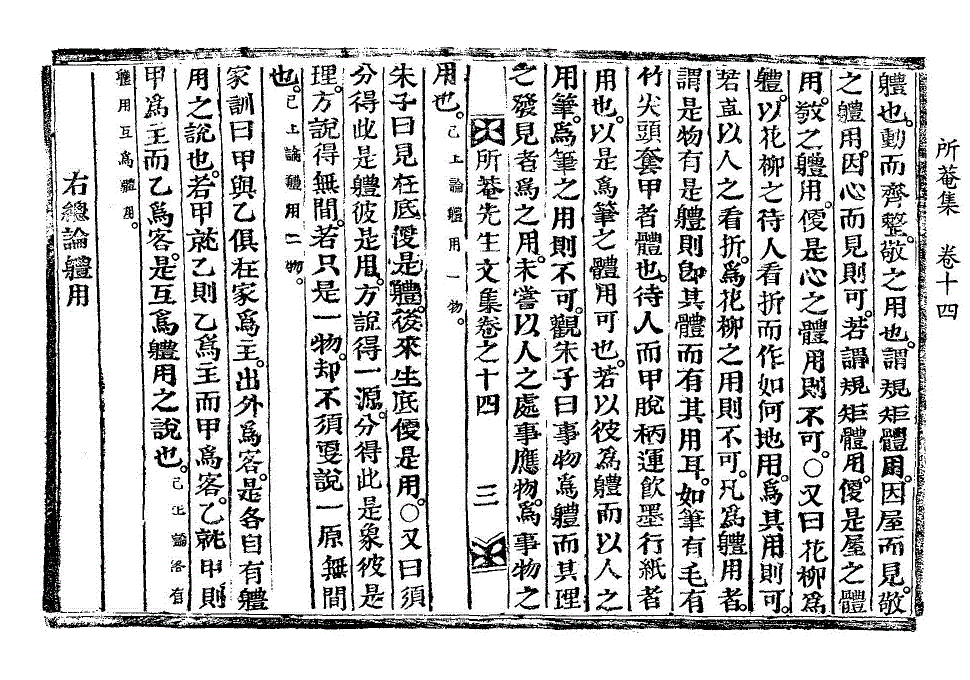 体也。动而齐整。敬之用也。谓规矩体用。因屋而见。敬之体用。因心而见则可。若谓规矩体用。便是屋之体用。敬之体用。便是心之体用则不可。○又曰花柳为体。以花柳之待人看折而作如何地用。为其用则可。若直以人之看折。为花柳之用则不可。凡为体用者。谓是物有是体则即其体而有其用耳。如笔有毛有竹尖头套甲者体也。待人而甲脱柄运饮墨行纸者用也。以是为笔之体用可也。若以彼为体而以人之用笔。为笔之用则不可。观朱子曰事物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未尝以人之处事应物。为事物之用也。(已上论体用一物。)
体也。动而齐整。敬之用也。谓规矩体用。因屋而见。敬之体用。因心而见则可。若谓规矩体用。便是屋之体用。敬之体用。便是心之体用则不可。○又曰花柳为体。以花柳之待人看折而作如何地用。为其用则可。若直以人之看折。为花柳之用则不可。凡为体用者。谓是物有是体则即其体而有其用耳。如笔有毛有竹尖头套甲者体也。待人而甲脱柄运饮墨行纸者用也。以是为笔之体用可也。若以彼为体而以人之用笔。为笔之用则不可。观朱子曰事物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未尝以人之处事应物。为事物之用也。(已上论体用一物。)朱子曰见在底便是体。后来生底便是用。○又曰须分得此是体彼是用。方说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说得无间。若只是一物。却不须更说一原无间也。(已上论体用二物。)
家训曰甲与乙俱在家为主。出外为客。是各自有体用之说也。若甲就乙则乙为主而甲为客。乙就甲则甲为主而乙为客。是互为体用之说也。(已上论各有体用互为体用。)
(右总论体用)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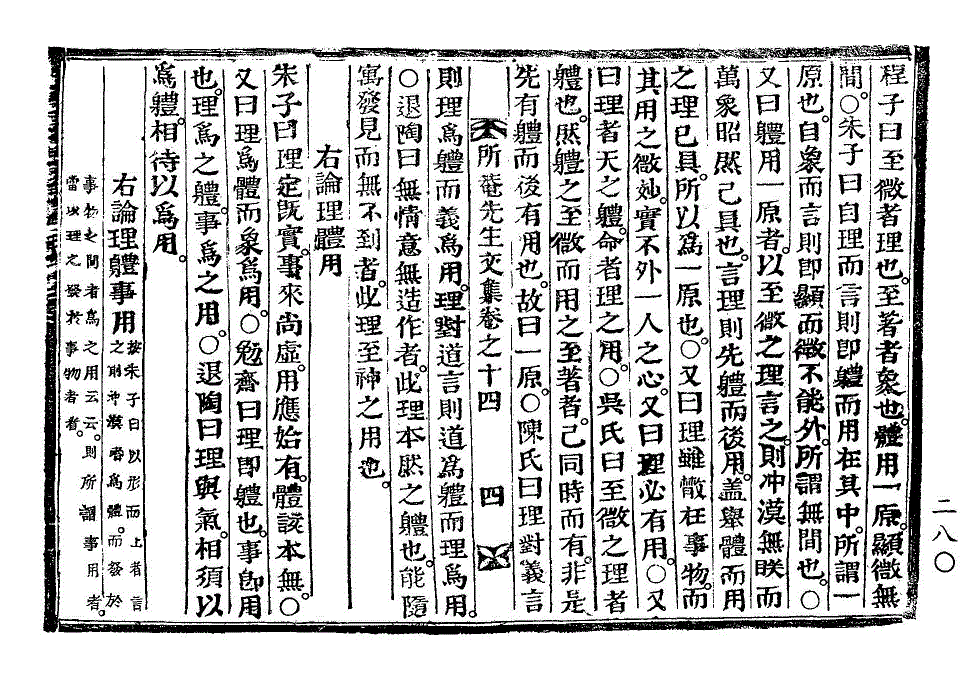 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朱子曰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又曰体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眹而万象昭然已具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所以为一原也。○又曰理虽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一人之心。又曰理必有用。○又曰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吴氏曰至微之理者体也。然体之至微而用之至著者。已同时而有。非是先有体而后有用也。故曰一原。○陈氏曰理对义言则理为体而义为用。理对道言则道为体而理为用。○退陶曰无情意无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能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
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朱子曰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又曰体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眹而万象昭然已具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所以为一原也。○又曰理虽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一人之心。又曰理必有用。○又曰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吴氏曰至微之理者体也。然体之至微而用之至著者。已同时而有。非是先有体而后有用也。故曰一原。○陈氏曰理对义言则理为体而义为用。理对道言则道为体而理为用。○退陶曰无情意无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能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右论理体用)
朱子曰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又曰理为体而象为用。○勉斋曰理即体也。事即用也。理为之体。事为之用。○退陶曰理与气。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
(右论理体事用 按朱子曰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为体。而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云云。则所谓事用者。当以理之发于事物者看。)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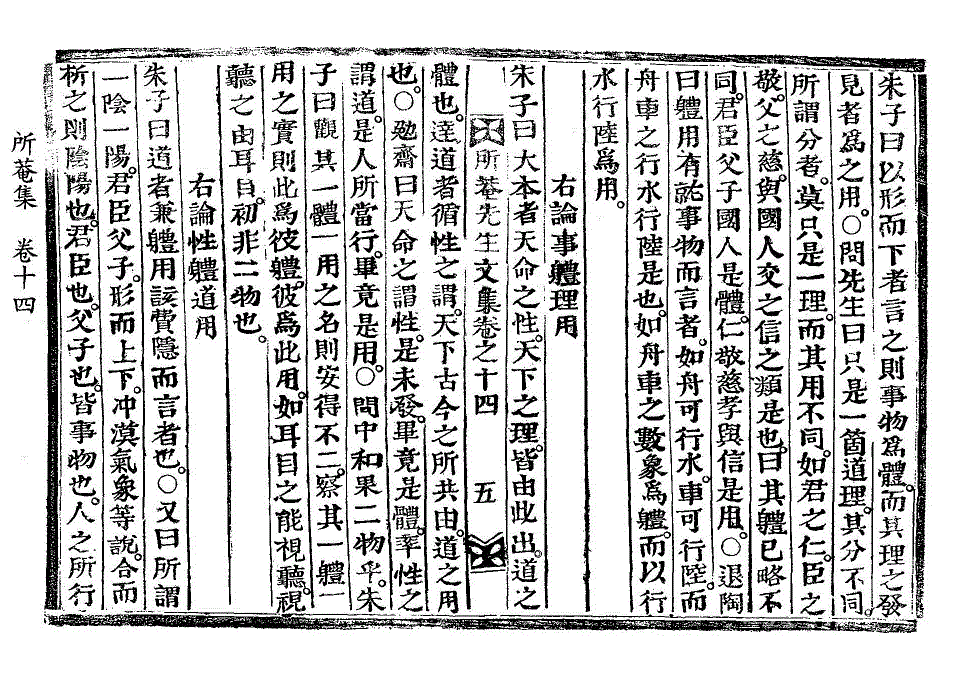 朱子曰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问先生曰只是一个道理。其分不同。所谓分者。莫只是一理。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与国人交之信之类是也。曰其体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国人是体。仁敬慈孝与信是用。○退陶曰体用有就事物而言者。如舟可行水。车可行陆。而舟车之行水行陆是也。如舟车之数象为体。而以行水行陆为用。
朱子曰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问先生曰只是一个道理。其分不同。所谓分者。莫只是一理。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与国人交之信之类是也。曰其体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国人是体。仁敬慈孝与信是用。○退陶曰体用有就事物而言者。如舟可行水。车可行陆。而舟车之行水行陆是也。如舟车之数象为体。而以行水行陆为用。(右论事体理用)
朱子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勉斋曰天命之谓性。是未发。毕竟是体。率性之谓道。是人所当行。毕竟是用。○问中和果二物乎。朱子曰观其一体一用之名则安得不二。察其一体一用之实则此为彼体。彼为此用。如耳目之能视听。视听之由耳目。初非二物也。
(右论性体道用)
朱子曰道者兼体用该费隐而言者也。○又曰所谓一阴一阳。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气象等说。合而析之则阴阳也。君臣也。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1L 页
 也。形而下者也。万象之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若以形而下云云。不可槩谓。形而上者谓道之体。天下之达道五。为道之用也。○又曰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勉斋曰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退陶曰道理有动有静。故指其静者为体。指其动者为用。道理动静之实。即道理体用之实也。夫体用有二。有就道理而言者。有就事物而言者。
也。形而下者也。万象之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若以形而下云云。不可槩谓。形而上者谓道之体。天下之达道五。为道之用也。○又曰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勉斋曰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退陶曰道理有动有静。故指其静者为体。指其动者为用。道理动静之实。即道理体用之实也。夫体用有二。有就道理而言者。有就事物而言者。(右论道自有体用)
朱子曰如说性之用是情。○又曰仁存诸心。情之所以为体也。义制夫事。性之所以为用也。以性言之则皆体也。以情言之则皆用也。以阴阳言之则义体而仁用也。○家训曰以阴阳言则义智为体。仁礼为用。以内外言则仁礼为体。义智为用。
(右论性自有体用)
朱子曰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又曰费道之用也。隐道之体也。用则理之见于日用。无不可见也。体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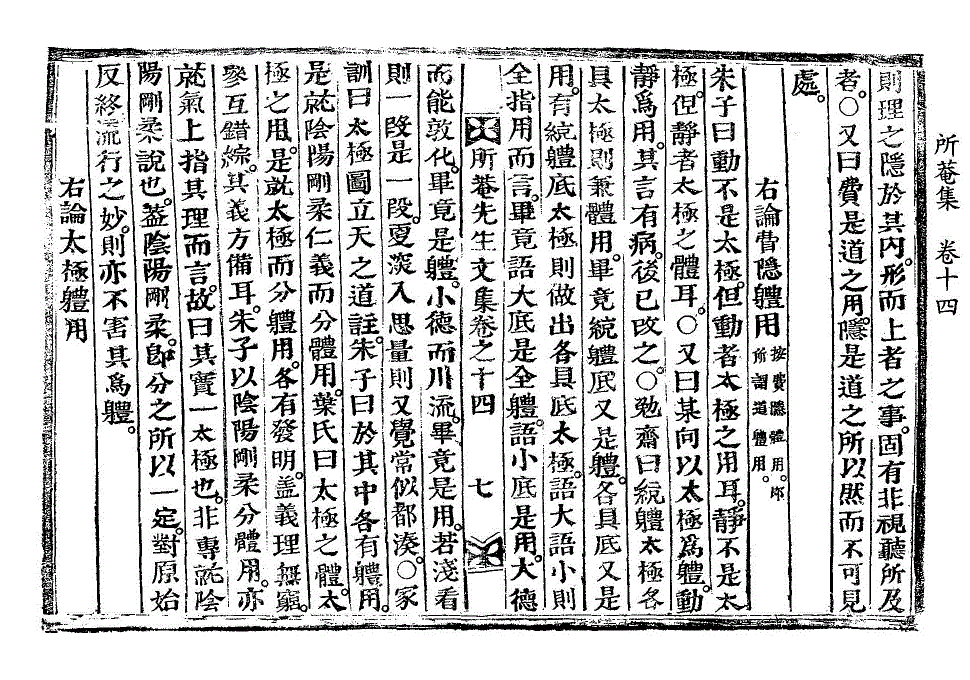 则理之隐于其内。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视听所及者。○又曰费是道之用。隐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见处。
则理之隐于其内。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视听所及者。○又曰费是道之用。隐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见处。(右论费隐体用 按费隐体用。即所谓道体用。)
朱子曰动不是太极。但动者太极之用耳。静不是太极。但静者太极之体耳。○又曰某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其言有病。后已改之。○勉斋曰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则兼体用。毕竟统体底又是体。各具底又是用。有统体底太极则做出各具底太极。语大语小则全指用而言。毕竟语大底是全体。语小底是用。大德而能敦化。毕竟是体。小德而川流。毕竟是用。若浅看则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则又觉常似都凑。○家训曰太极图立天之道注。朱子曰于其中各有体用。是就阴阳刚柔仁义而分体用。叶氏曰太极之体。太极之用。是就太极而分体用。各有发明。盖义理无穷。参互错综。其义方备耳。朱子以阴阳刚柔分体用。亦就气上指其理而言。故曰其实一太极也。非专就阴阳刚柔说也。盖阴阳刚柔。即分之所以一定。对原始反终流行之妙。则亦不害其为体。
(右论太极体用)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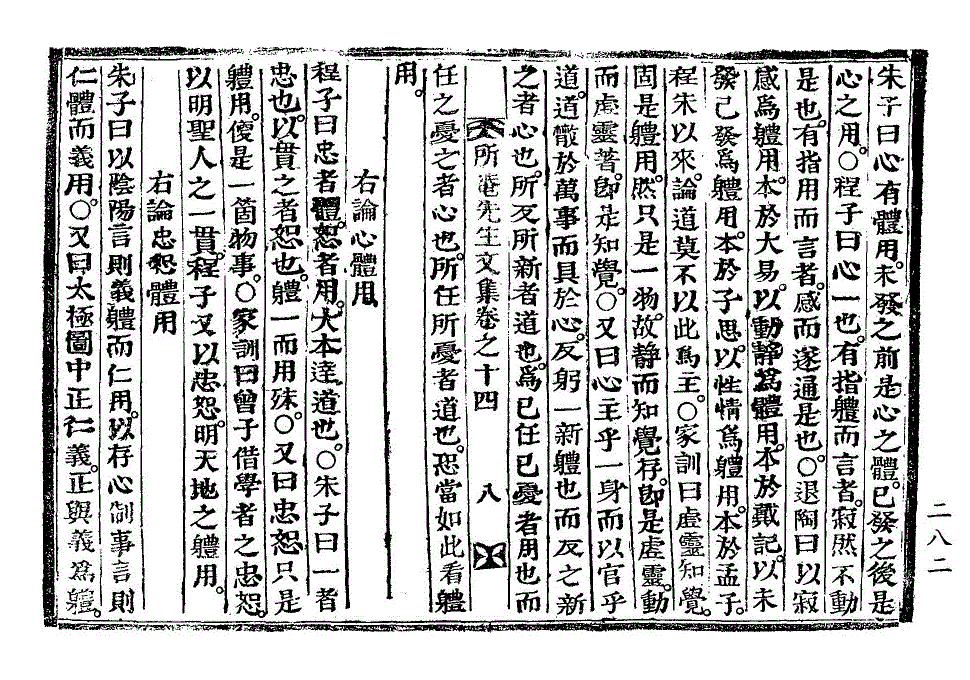 朱子曰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后是心之用。○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退陶曰以寂感为体用。本于大易。以动静为体用。本于戴记。以未发已发为体用。本于子思。以性情为体用。本于孟子。程朱以来。论道莫不以此为主。○家训曰虚灵知觉。固是体用。然只是一物。故静而知觉存。即是虚灵。动而虚灵著。即是知觉。○又曰心主乎一身而以官乎道。道散于万事而具于心。反躬一新体也而反之新之者心也。所反所新者道也。为己任己忧者用也而任之忧之者心也。所任所忧者道也。恐当如此看体用。
朱子曰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后是心之用。○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退陶曰以寂感为体用。本于大易。以动静为体用。本于戴记。以未发已发为体用。本于子思。以性情为体用。本于孟子。程朱以来。论道莫不以此为主。○家训曰虚灵知觉。固是体用。然只是一物。故静而知觉存。即是虚灵。动而虚灵著。即是知觉。○又曰心主乎一身而以官乎道。道散于万事而具于心。反躬一新体也而反之新之者心也。所反所新者道也。为己任己忧者用也而任之忧之者心也。所任所忧者道也。恐当如此看体用。(右论心体用)
程子曰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朱子曰一者忠也。以贯之者恕也。体一而用殊。○又曰忠恕只是体用。便是一个物事。○家训曰曾子借学者之忠恕。以明圣人之一贯。程子又以忠恕。明天地之体用。
(右论忠恕体用)
朱子曰以阴阳言则义体而仁用。以存心制事言则仁体而义用。○又曰太极图中正仁义。正与义为体。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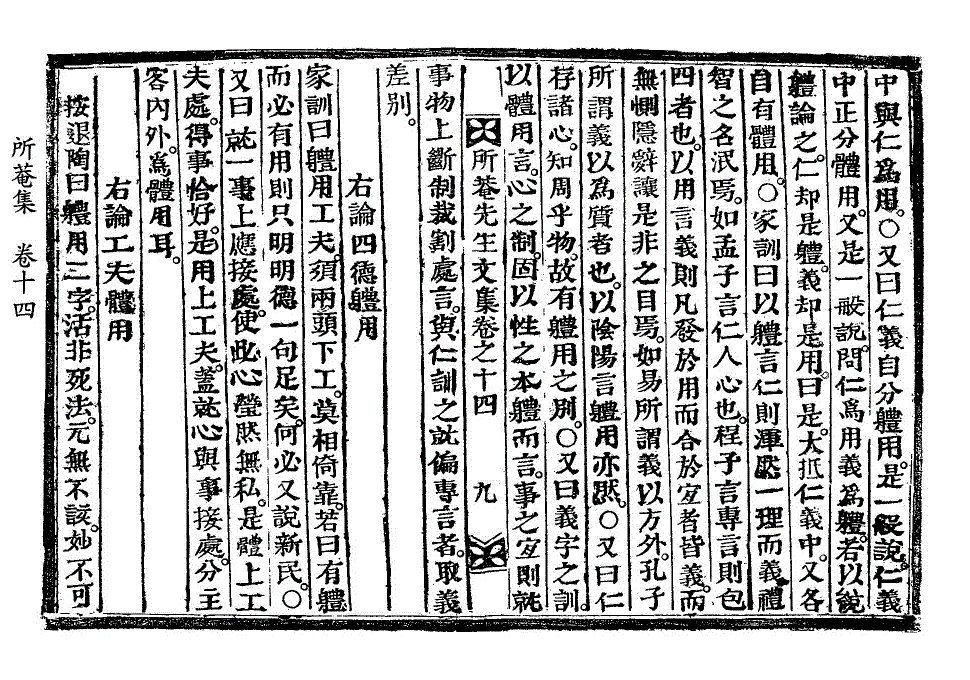 中与仁为用。○又曰仁义自分体用。是一般说。仁义中正分体用。又是一般说。问仁为用义为体。若以统体论之。仁却是体。义却是用。曰是。大抵仁义中。又各自有体用。○家训曰以体言仁则浑然一理而义礼智之名泯焉。如孟子言仁人心也。程子言专言则包四者也。以用言义则凡发于用而合于宜者皆义。而无恻隐辞让是非之目焉。如易所谓义以方外。孔子所谓义以为质者也。以阴阳言体用亦然。○又曰仁存诸心。知周乎物。故有体用之别。○又曰义字之训。以体用言。心之制。固以性之本体而言。事之宜则就事物上断制裁割处言。与仁训之就偏专言者。取义差别。
中与仁为用。○又曰仁义自分体用。是一般说。仁义中正分体用。又是一般说。问仁为用义为体。若以统体论之。仁却是体。义却是用。曰是。大抵仁义中。又各自有体用。○家训曰以体言仁则浑然一理而义礼智之名泯焉。如孟子言仁人心也。程子言专言则包四者也。以用言义则凡发于用而合于宜者皆义。而无恻隐辞让是非之目焉。如易所谓义以方外。孔子所谓义以为质者也。以阴阳言体用亦然。○又曰仁存诸心。知周乎物。故有体用之别。○又曰义字之训。以体用言。心之制。固以性之本体而言。事之宜则就事物上断制裁割处言。与仁训之就偏专言者。取义差别。(右论四德体用)
家训曰体用工夫。须两头下工。莫相倚靠。若曰有体而必有用则只明明德一句足矣。何必又说新民。○又曰就一事上应接处。使此心莹然无私。是体上工夫处。得事恰好。是用上工夫。盖就心与事接处。分主客内外。为体用耳。
(右论工夫体用)
按退陶曰体用二字。活非死法。元无不该。妙不可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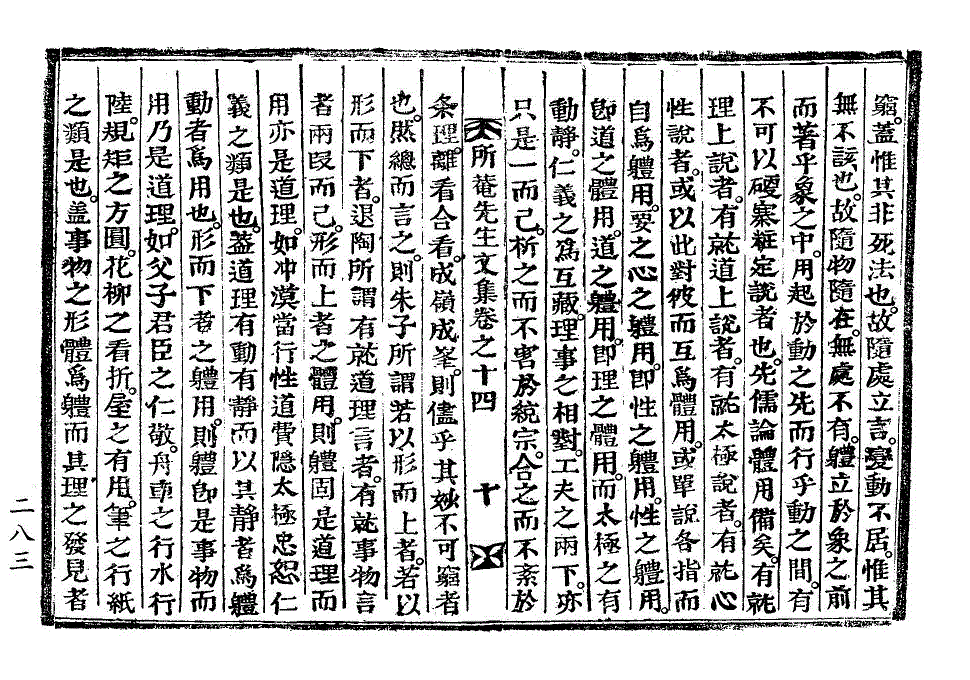 穷。盖惟其非死法也。故随处立言。变动不居。惟其无不该也。故随物随在。无处不有。体立于象之前而著乎象之中。用起于动之先而行乎动之间。有不可以硬寨妆定说者也。先儒论体用备矣。有就理上说者。有就道上说者。有就太极说者。有就心性说者。或以此对彼而互为体用。或单说各指而自为体用。要之心之体用。即性之体用。性之体用。即道之体用。道之体用。即理之体用。而太极之有动静。仁义之为互藏。理事之相对。工夫之两下。亦只是一而已。析之而不害于统宗。合之而不紊于条理。离看合看。成岭成峰。则尽乎其妙不可穷者也。然总而言之。则朱子所谓若以形而上者。若以形而下者。退陶所谓有就道理言者。有就事物言者两段而已。形而上者之体用。则体固是道理而用亦是道理。如冲漠当行性道费隐太极忠恕仁义之类是也。盖道理有动有静而以其静者为体动者为用也。形而下者之体用。则体即是事物而用乃是道理。如父子君臣之仁敬。舟车之行水行陆。规矩之方圆。花柳之看折。屋之有用。笔之行纸之类是也。盖事物之形体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
穷。盖惟其非死法也。故随处立言。变动不居。惟其无不该也。故随物随在。无处不有。体立于象之前而著乎象之中。用起于动之先而行乎动之间。有不可以硬寨妆定说者也。先儒论体用备矣。有就理上说者。有就道上说者。有就太极说者。有就心性说者。或以此对彼而互为体用。或单说各指而自为体用。要之心之体用。即性之体用。性之体用。即道之体用。道之体用。即理之体用。而太极之有动静。仁义之为互藏。理事之相对。工夫之两下。亦只是一而已。析之而不害于统宗。合之而不紊于条理。离看合看。成岭成峰。则尽乎其妙不可穷者也。然总而言之。则朱子所谓若以形而上者。若以形而下者。退陶所谓有就道理言者。有就事物言者两段而已。形而上者之体用。则体固是道理而用亦是道理。如冲漠当行性道费隐太极忠恕仁义之类是也。盖道理有动有静而以其静者为体动者为用也。形而下者之体用。则体即是事物而用乃是道理。如父子君臣之仁敬。舟车之行水行陆。规矩之方圆。花柳之看折。屋之有用。笔之行纸之类是也。盖事物之形体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4H 页
 为用也。以形上则体用具是理。以形下则体事而用理何也。理不待事而有是体者必有是用。朱子所谓理有动静。程子所谓体用一原也。事必有理而事之有用。即理之有用。朱子所谓发于事物。程子所谓显微无间也。理大而事小。理尊而事卑。理无乎不在而事有所限。于此亦可见矣。今辄摭取先儒言体用者十二条。馀可类推而得也。
为用也。以形上则体用具是理。以形下则体事而用理何也。理不待事而有是体者必有是用。朱子所谓理有动静。程子所谓体用一原也。事必有理而事之有用。即理之有用。朱子所谓发于事物。程子所谓显微无间也。理大而事小。理尊而事卑。理无乎不在而事有所限。于此亦可见矣。今辄摭取先儒言体用者十二条。馀可类推而得也。一介山人说
一介山者。大夕山之释名也。山自公山而下。窄田而起。无枝脚屈曲。厚重质直。独一介出大野中。俗之相呼。意其以此。而名之为大夕。所以文之也。其西南为吾世居之地。其北之燕为天荒。吾祖尝有意焉而未就。余以先躅之故。经营且数十年。壬辰春。赖同人助力。始得诛茅焉。取其幽僻閒旷也。余以一介身。于世鲜缘。每独出而当众之冲。其气象与玆山者类。遂因其俗号而自命为一介山人。秦穆之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容者德之量也。有量则弘。弘则长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惟仁无对。此其为一介乎。山无奇岩侧壁窈窕媚悦之观。而重厚平夷。气完而蓄厚。所谓断断兮无他技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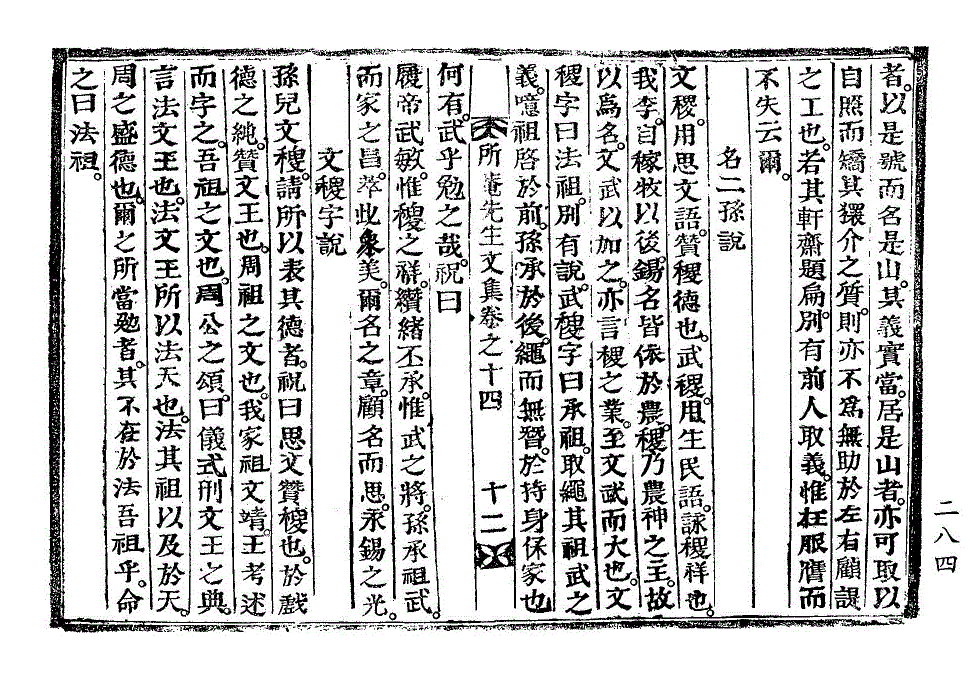 者。以是号而名是山。其义实当。居是山者。亦可取以自照而矫其獧介之质。则亦不为无助于左右顾諟之工也。若其轩斋题扁。别有前人取义。惟在服膺而不失云尔。
者。以是号而名是山。其义实当。居是山者。亦可取以自照而矫其獧介之质。则亦不为无助于左右顾諟之工也。若其轩斋题扁。别有前人取义。惟在服膺而不失云尔。名二孙说
文稷。用思文语。赞稷德也。武稷。用生民语。咏稷祥也。我李。自稼牧以后。锡名皆依于农。稷乃农神之主。故以为名。文武以加之。亦言稷之业。至文武而大也。文稷字曰法祖。别有说。武稷字曰承祖。取绳其祖武之义。噫祖启于前。孙承于后。绳而无替。于持身保家也何有。武乎勉之哉。祝曰。
履帝武敏。惟稷之祥。缵绪丕承。惟武之将。孙承祖武。而家之昌。萃此众美。尔名之章。顾名而思。永锡之光。
文稷字说
孙儿文稷。请所以表其德者。祝曰思文赞稷也。于戏德之纯。赞文王也。周祖之文也。我家祖文靖。王考述而字之。吾之文也。周公之颂。曰仪式刑文王之典。言法文王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法其祖以及于天。周之盛德也。尔之所当勉者。其不在于法吾祖乎。命之曰法祖。
姜汉奎字说
姜君汉奎。字曰汉五。取星瑞也。五行之气。会而文明应。故聚井为汉。聚奎为宋。文之先见者也。人禀五行之秀而具五性之德。德聚而文著。则天又在人矣。锡名之义。其在兹乎。然天何尝无五星。而聚而后文兆。人何尝无五性。而修而后德全。修于己以俟天。存乎其人。汉五勉乎哉。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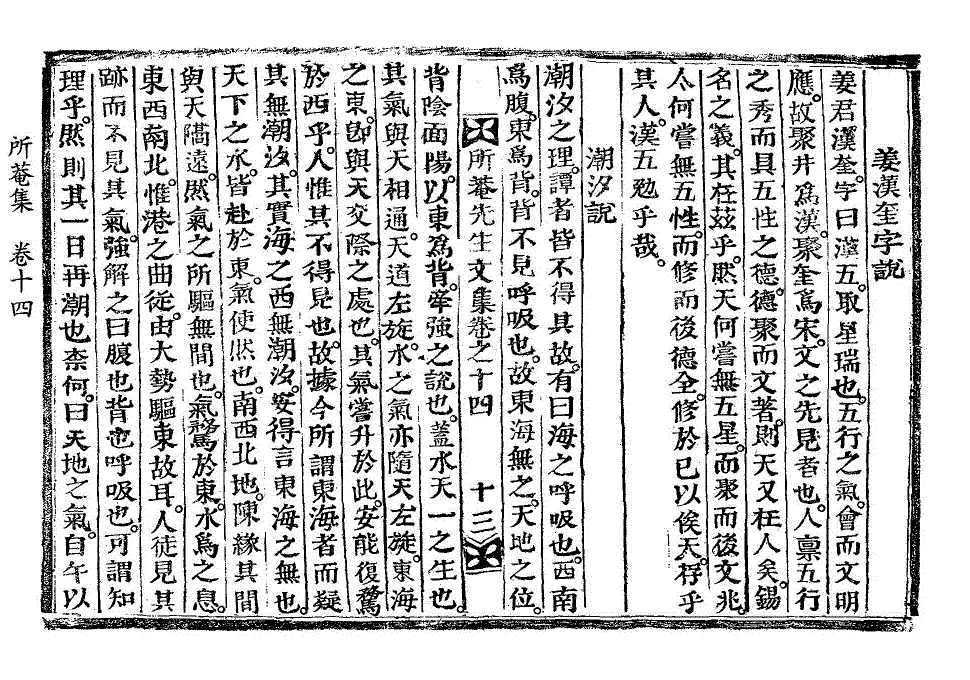 潮汐说
潮汐说潮汐之理。谭者皆不得其故。有曰海之呼吸也。西南为腹。东为背。背不见呼吸也。故东海无之。天地之位。背阴面阳。以东为背。牵强之说也。盖水天一之生也。其气与天相通。天道左旋。水之气亦随天左旋。东海之东。即与天交际之处也。其气尝升于此。安能复骛于西乎。人惟其不得见也。故据今所谓东海者而疑其无潮汐。其实海之西无潮汐。安得言东海之无也。天下之水。皆赴于东。气使然也。南西北地。陈缘其间与天隔远。然气之所驱无间也。气骛于东。水为之息。东西南北。惟港之曲从。由大势驱东故耳。人徒见其迹而不见其气。强解之曰腹也背也呼吸也。可谓知理乎。然则其一日再潮也柰何。曰天地之气。自午以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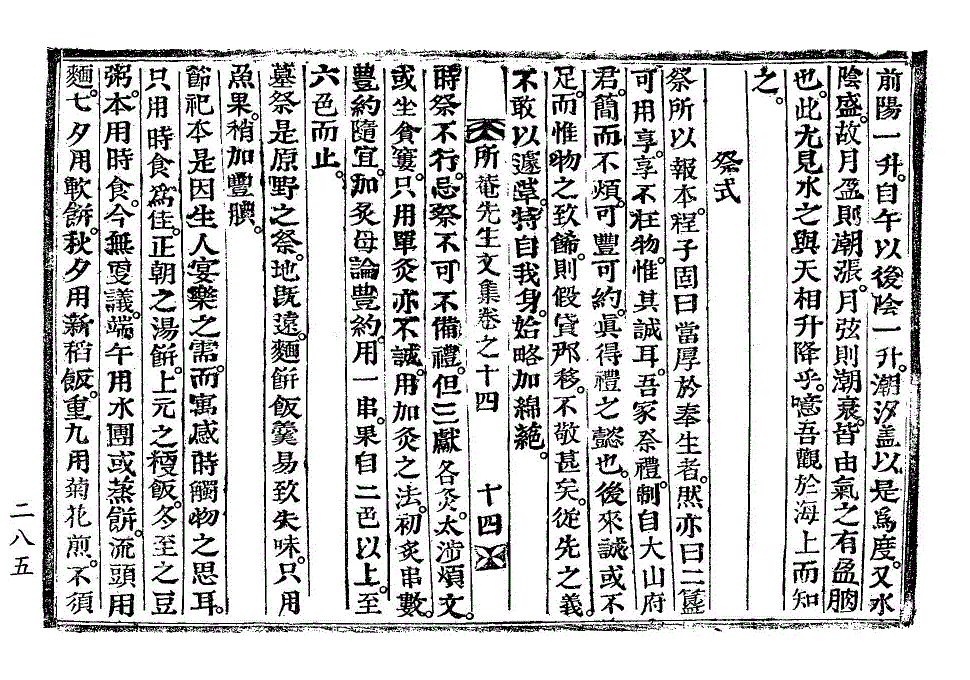 前阳一升。自午以后阴一升。潮汐盖以是为度。又水阴盛。故月盈则潮涨。月弦则朝衰。皆由气之有盈朒也。此尤见水之与天相升降乎。噫吾观于海上而知之。
前阳一升。自午以后阴一升。潮汐盖以是为度。又水阴盛。故月盈则潮涨。月弦则朝衰。皆由气之有盈朒也。此尤见水之与天相升降乎。噫吾观于海上而知之。祭式
祭所以报本。程子固曰当厚于奉生者。然亦曰二簋可用享。享不在物。惟其诚耳。吾家祭礼。制自大山府君。简而不烦。可丰可约。真得礼之懿也。后来诚或不足。而惟物之致饰。则假贷那移。不敬甚矣。从先之义。不敢以遽革。特自我身。始略加绵蕝。
时祭不行。忌祭不可不备礼。但三献各炙。太涉烦文。或坐贫窭。只用单炙亦不诚。用加炙之法。初炙串数。礼约随宜。加炙毋论礼约。用一串。果自二色以上。至六色而止。
墓祭是原野之祭。地既远。面饼饭羹易致失味。只用鱼果。稍加丰腆。
节祀本是因生人宴乐之需。而寓感时触物之思耳。只用时食为佳。正朝之汤饼。上元之粳饭。冬至之豆粥。本用时食。今无更议。端午用水团或蒸饼。流头用面。七夕用软饼。秋夕用新稻饭。重九用菊花煎。不须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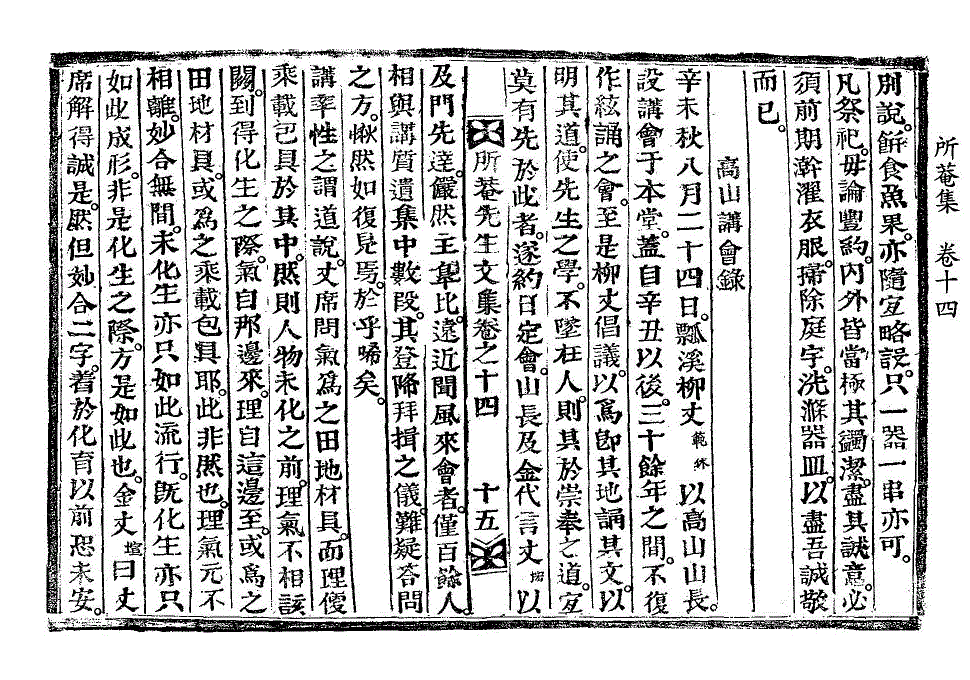 别说。饼食鱼果。亦随宜略设。只一器一串亦可。
别说。饼食鱼果。亦随宜略设。只一器一串亦可。凡祭祀。毋论丰约。内外皆当极其蠲洁。尽其诚意。必须前期浣濯衣服。扫除庭宇。洗涤器皿。以尽吾诚敬而已。
高山讲会录
辛未秋八月二十四日。瓢溪柳丈(范休)以高山山长。设讲会于本堂。盖自辛丑以后。三十馀年之间。不复作弦诵之会。至是柳丈倡议。以为即其地诵其文。以明其道。使先生之学。不坠在人。则其于崇奉之道。宜莫有先于此者。遂约日定会。山长及金代言丈(㙆)以及门先达。俨然主皋比。远近闻风来会者。仅百馀人。相与讲质遗集中数段。其登降拜揖之仪。难疑答问之方。愀然如复见焉。于乎唏矣。
讲率性之谓道说。丈席问气为之田地材具。而理便乘载包具于其中。然则人物未化之前。理气不相该关。到得化生之际。气自那边来。理自这边至。或为之田地材具。或为之乘载包具耶。此非然也。理气元不相离。妙合无间。未化生亦只如此流行。既化生亦只如此成形。非是化生之际。方是如此也。金丈(塇)曰丈席解得诚是。然但妙合二字。着于化育以前恐未安。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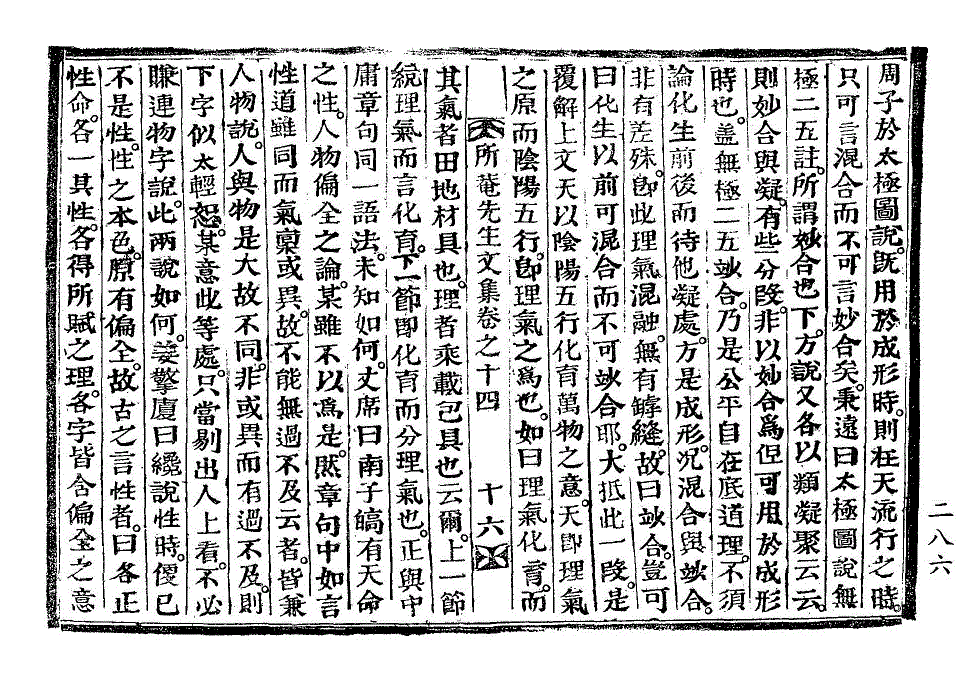 周子于太极图说。既用于成形时。则在天流行之时。只可言混合而不可言妙合矣。秉远曰太极图说无极二五注。所谓妙合也下。方说又各以类凝聚云云。则妙合与凝。有些分段。非以妙合为但可用于成形时也。盖无极二五妙合。乃是公平自在底道理。不须论化生前后而待他凝处。方是成形。况混合与妙合。非有差殊。即此理气混融。无有罅缝。故曰妙合。岂可曰化生以前可混合而不可妙合耶。大抵此一段。是覆解上文天以阴阳五行化育万物之意。天即理气之原而阴阳五行。即理气之为也。如曰理气化育。而其气者田地材具也。理者乘载包具也云尔。上一节统理气而言化育。下一节即化育而分理气也。正与中庸章句同一语法。未知如何。丈席曰南子皓有天命之性。人物偏全之论。某虽不以为是。然章句中如言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云者。皆兼人物说。人与物是大故不同。非或异而有过不及。则下字似太轻恕。某意此等处。只当剔出人上看。不必赚连物字说。此两说如何。姜擎厦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性之本色。原有偏全。故古之言性者。曰各正性命。各一其性。各得所赋之理。各字皆含偏全之意
周子于太极图说。既用于成形时。则在天流行之时。只可言混合而不可言妙合矣。秉远曰太极图说无极二五注。所谓妙合也下。方说又各以类凝聚云云。则妙合与凝。有些分段。非以妙合为但可用于成形时也。盖无极二五妙合。乃是公平自在底道理。不须论化生前后而待他凝处。方是成形。况混合与妙合。非有差殊。即此理气混融。无有罅缝。故曰妙合。岂可曰化生以前可混合而不可妙合耶。大抵此一段。是覆解上文天以阴阳五行化育万物之意。天即理气之原而阴阳五行。即理气之为也。如曰理气化育。而其气者田地材具也。理者乘载包具也云尔。上一节统理气而言化育。下一节即化育而分理气也。正与中庸章句同一语法。未知如何。丈席曰南子皓有天命之性。人物偏全之论。某虽不以为是。然章句中如言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云者。皆兼人物说。人与物是大故不同。非或异而有过不及。则下字似太轻恕。某意此等处。只当剔出人上看。不必赚连物字说。此两说如何。姜擎厦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性之本色。原有偏全。故古之言性者。曰各正性命。各一其性。各得所赋之理。各字皆含偏全之意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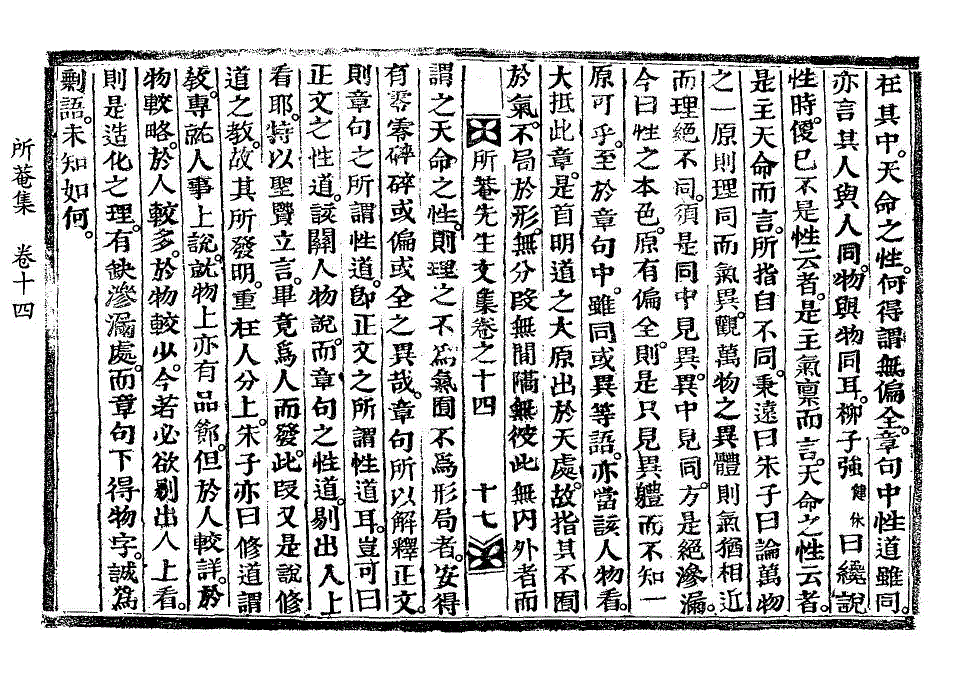 在其中。天命之性。何得谓无偏全。章句中性道虽同。亦言其人与人同。物与物同耳。柳子强(健休)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云者。是主气禀而言。天命之性云者。是主天命而言。所指自不同。秉远曰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须是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方是绝渗漏。今曰性之本色。原有偏全。则是只见异体而不知一原可乎。至于章句中。虽同或异等语。亦当该人物看。大抵此章。是首明道之大原出于天处。故指其不囿于气。不局于形。无分段无间隔无彼此无内外者而谓之天命之性。则理之不为气囿不为形局者。安得有零零碎碎或偏或全之异哉。章句所以解释正文。则章句之所谓性道。即正文之所谓性道耳。岂可曰正文之性道。该关人物说。而章句之性道。剔出人上看耶。特以圣贤立言。毕竟为人而发。此段又是说修道之教。故其所发明。重在人分上。朱子亦曰修道谓教。专就人事上说。就物上亦有品节。但于人较详。于物较略。于人较多。于物较少。今若必欲剔出人上看。则是造化之理。有缺渗漏处。而章句下得物字。诚为剩语。未知如何。
在其中。天命之性。何得谓无偏全。章句中性道虽同。亦言其人与人同。物与物同耳。柳子强(健休)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云者。是主气禀而言。天命之性云者。是主天命而言。所指自不同。秉远曰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须是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方是绝渗漏。今曰性之本色。原有偏全。则是只见异体而不知一原可乎。至于章句中。虽同或异等语。亦当该人物看。大抵此章。是首明道之大原出于天处。故指其不囿于气。不局于形。无分段无间隔无彼此无内外者而谓之天命之性。则理之不为气囿不为形局者。安得有零零碎碎或偏或全之异哉。章句所以解释正文。则章句之所谓性道。即正文之所谓性道耳。岂可曰正文之性道。该关人物说。而章句之性道。剔出人上看耶。特以圣贤立言。毕竟为人而发。此段又是说修道之教。故其所发明。重在人分上。朱子亦曰修道谓教。专就人事上说。就物上亦有品节。但于人较详。于物较略。于人较多。于物较少。今若必欲剔出人上看。则是造化之理。有缺渗漏处。而章句下得物字。诚为剩语。未知如何。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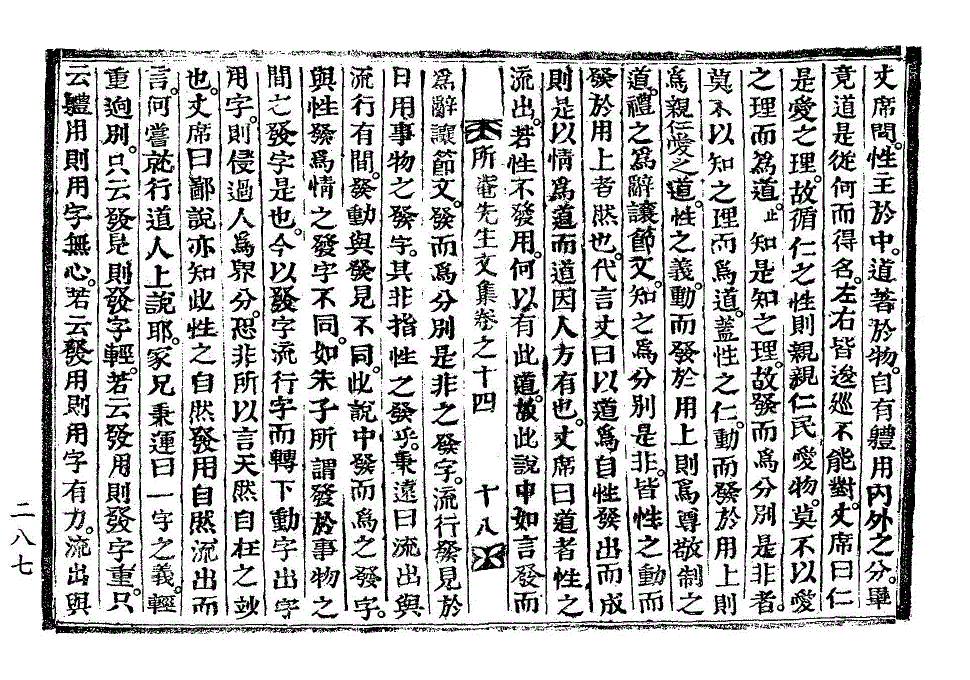 丈席问。性主于中。道著于物。自有体用内外之分。毕竟道是从何而得名。左右皆逡巡不能对。丈席曰仁是爱之理。故循仁之性则亲亲仁民爱物。莫不以爱之理而为道。(止)知是知之理。故发而为分别是非者。莫不以知之理而为道。盖性之仁。动而发于用上则为亲仁爱之道。性之义。动而发于用上则为尊敬制之道。礼之为辞让节文。知之为分别是非。皆性之动而发于用上者然也。代言丈曰以道为自性发出而成则是以情为道而道因人方有也。丈席曰道者性之流出。若性不发用。何以有此道。故此说中如言发而为辞让节文。发而为分别是非之发字。流行发见于日用事物之发字。其非指性之发乎。秉远曰流出与流行有间。发动与发见不同。此说中发而为之发字。与性发为情之发字不同。如朱子所谓发于事物之间之发字是也。今以发字流行字而转下动字出字用字。则侵过人为界分。恐非所以言天然自在之妙也。丈席曰鄙说亦知此性之自然发用自然流出而言。何尝就行道人上说耶。家兄秉运曰一字之义。轻重迥别。只云发见则发字轻。若云发用则发字重。只云体用则用字无心。若云发用则用字有力。流出与
丈席问。性主于中。道著于物。自有体用内外之分。毕竟道是从何而得名。左右皆逡巡不能对。丈席曰仁是爱之理。故循仁之性则亲亲仁民爱物。莫不以爱之理而为道。(止)知是知之理。故发而为分别是非者。莫不以知之理而为道。盖性之仁。动而发于用上则为亲仁爱之道。性之义。动而发于用上则为尊敬制之道。礼之为辞让节文。知之为分别是非。皆性之动而发于用上者然也。代言丈曰以道为自性发出而成则是以情为道而道因人方有也。丈席曰道者性之流出。若性不发用。何以有此道。故此说中如言发而为辞让节文。发而为分别是非之发字。流行发见于日用事物之发字。其非指性之发乎。秉远曰流出与流行有间。发动与发见不同。此说中发而为之发字。与性发为情之发字不同。如朱子所谓发于事物之间之发字是也。今以发字流行字而转下动字出字用字。则侵过人为界分。恐非所以言天然自在之妙也。丈席曰鄙说亦知此性之自然发用自然流出而言。何尝就行道人上说耶。家兄秉运曰一字之义。轻重迥别。只云发见则发字轻。若云发用则发字重。只云体用则用字无心。若云发用则用字有力。流出与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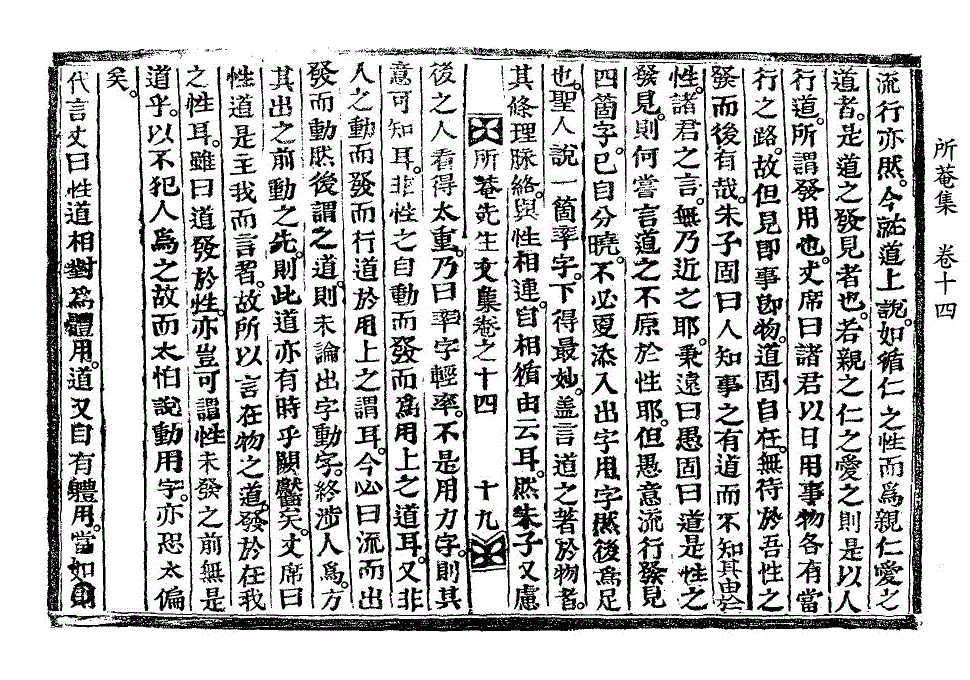 流行亦然。今就道上说。如循仁之性而为亲仁爱之道者。是道之发见者也。若亲之仁之爱之则是以人行道。所谓发用也。丈席曰诸君以日用事物各有当行之路。故但见即事即物。道固自在。无待于吾性之发而后有哉。朱子固曰人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诸君之言。无乃近之耶。秉远曰愚固曰道是性之发见。则何尝言道之不原于性耶。但愚意流行发见四个字。已自分晓。不必更添入出字用字然后为足也。圣人说一个率字。下得最妙。盖言道之著于物者。其条理脉络。与性相连。自相循由云耳。然朱子又虑后之人看得太重。乃曰率字轻率。不是用力字。则其意可知耳。非性之自动而发而为用上之道耳。又非人之动而发而行道于用上之谓耳。今必曰流而出发而动然后谓之道。则未论出字动字。终涉人为。方其出之前动之先。则此道亦有时乎阙齾矣。丈席曰性道是主我而言者。故所以言在物之道。发于在我之性耳。虽曰道发于性。亦岂可谓性未发之前无是道乎。以不犯人为之故而太怕说动用字。亦恐太偏矣。
流行亦然。今就道上说。如循仁之性而为亲仁爱之道者。是道之发见者也。若亲之仁之爱之则是以人行道。所谓发用也。丈席曰诸君以日用事物各有当行之路。故但见即事即物。道固自在。无待于吾性之发而后有哉。朱子固曰人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诸君之言。无乃近之耶。秉远曰愚固曰道是性之发见。则何尝言道之不原于性耶。但愚意流行发见四个字。已自分晓。不必更添入出字用字然后为足也。圣人说一个率字。下得最妙。盖言道之著于物者。其条理脉络。与性相连。自相循由云耳。然朱子又虑后之人看得太重。乃曰率字轻率。不是用力字。则其意可知耳。非性之自动而发而为用上之道耳。又非人之动而发而行道于用上之谓耳。今必曰流而出发而动然后谓之道。则未论出字动字。终涉人为。方其出之前动之先。则此道亦有时乎阙齾矣。丈席曰性道是主我而言者。故所以言在物之道。发于在我之性耳。虽曰道发于性。亦岂可谓性未发之前无是道乎。以不犯人为之故而太怕说动用字。亦恐太偏矣。代言丈曰性道相对为体用。道又自有体用。当如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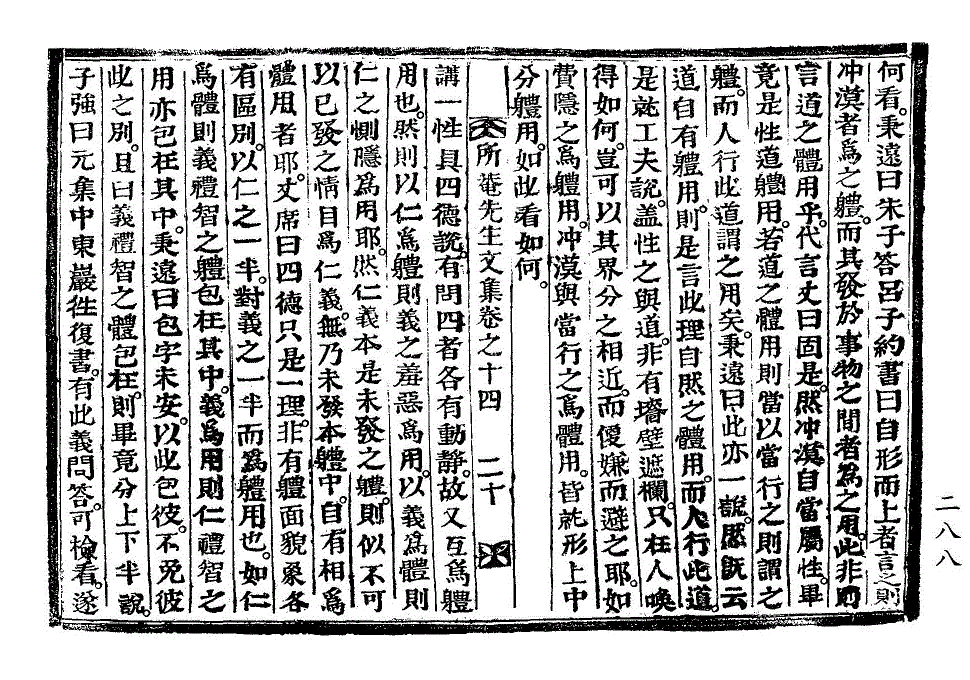 何看。秉远曰朱子答吕子约书曰自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为之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此非言道之体用乎。代言丈曰固是。然冲漠自当属性。毕竟是性道体用。若道之体用则当以当行之则谓之体。而人行此道谓之用矣。秉远曰此亦一说。然既云道自有体用。则是言此理自然之体用。而人行此道。是就工夫说。盖性之与道。非有墙壁遮栏。只在人唤得如何。岂可以其界分之相近。而便嫌而避之耶。如费隐之为体用。冲漠与当行之为体用。皆就形上中分体用。如此看如何。
何看。秉远曰朱子答吕子约书曰自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为之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此非言道之体用乎。代言丈曰固是。然冲漠自当属性。毕竟是性道体用。若道之体用则当以当行之则谓之体。而人行此道谓之用矣。秉远曰此亦一说。然既云道自有体用。则是言此理自然之体用。而人行此道。是就工夫说。盖性之与道。非有墙壁遮栏。只在人唤得如何。岂可以其界分之相近。而便嫌而避之耶。如费隐之为体用。冲漠与当行之为体用。皆就形上中分体用。如此看如何。讲一性具四德说。有问四者各有动静。故又互为体用也。然则以仁为体则义之羞恶为用。以义为体则仁之恻隐为用耶。然仁义本是未发之体。则似不可以已发之情目为仁义。无乃未发本体中。自有相为体用者耶。丈席曰四德只是一理。非有体面貌象各有区别。以仁之一半。对义之一半而为体用也。如仁为体则义礼智之体包在其中。义为用则仁礼智之用亦包在其中。秉远曰包字未安。以此包彼。不免彼此之别。且曰义礼智之体包在。则毕竟分上下半说。子强曰元集中东岩往复书。有此义问答。可检看。遂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9H 页
 取见元集。其略曰仁义固具于性而属乎静。然错而言之则发于用而见诸事者。亦通谓之仁义。故以性对情而言则仁义体而恻隐羞恶用也。若统言仁义而以存心制事言体用。则理之全具于心者即仁。而制事而适其宜者义也。以阴阳言体用则凝定敛藏于中者即义。而流动发达于外者仁也。其曰仁之体对义之用者。非以爱之理对羞恶之情而言也。谓以体言仁则浑然一理而义礼智之名泯焉。如孟子言仁人心也。以用言义则凡发于用而合宜者皆义而无恻隐辞让是非之目焉。如易所谓义以方外也。以阴阳言体用亦然。以其只是一理而各自有体用。故又有时而互为体用也。
取见元集。其略曰仁义固具于性而属乎静。然错而言之则发于用而见诸事者。亦通谓之仁义。故以性对情而言则仁义体而恻隐羞恶用也。若统言仁义而以存心制事言体用。则理之全具于心者即仁。而制事而适其宜者义也。以阴阳言体用则凝定敛藏于中者即义。而流动发达于外者仁也。其曰仁之体对义之用者。非以爱之理对羞恶之情而言也。谓以体言仁则浑然一理而义礼智之名泯焉。如孟子言仁人心也。以用言义则凡发于用而合宜者皆义而无恻隐辞让是非之目焉。如易所谓义以方外也。以阴阳言体用亦然。以其只是一理而各自有体用。故又有时而互为体用也。秉远问。温和慈爱宣著节文收敛裁断归藏凝定。一德必具两义。盖所以合天人而一之。如温和宣著收敛归藏衬元亨利贞慈爱节文裁断凝定。衬仁义礼智否。仲兄秉进曰不须如此说。凡属四德名目。欲其周遍纤悉。故每德辄用两目。何可分天人看。丈席曰亦略有此意思。不可全然打破。盖两说俱好。前说精致。后说活络耳。
柳公晦(徽文)问。此心之始发者仁。(止)恻隐之始发者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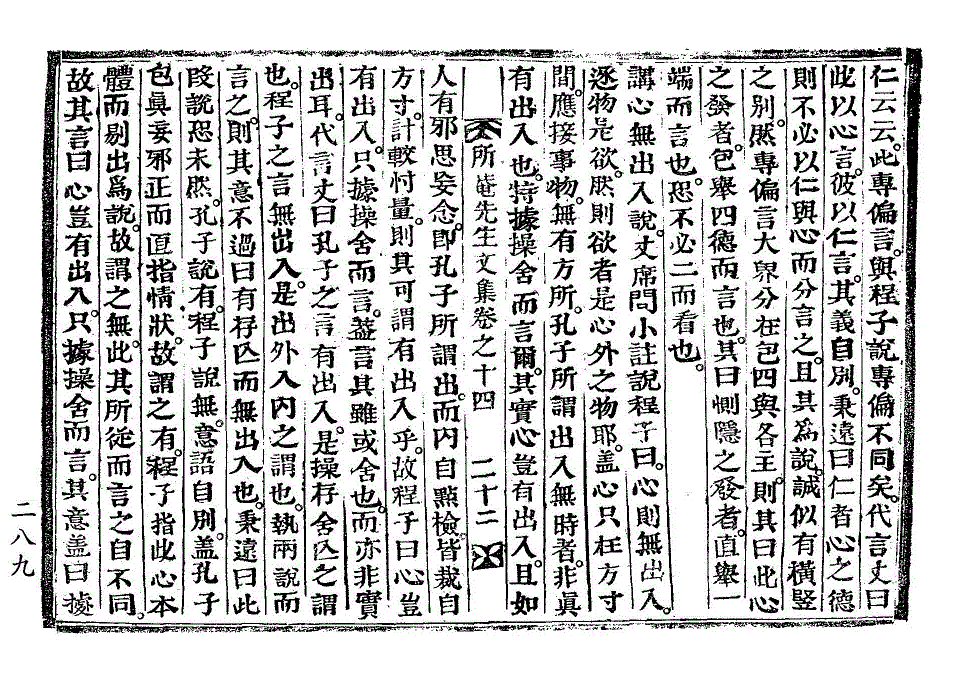 仁云云。此专偏言。与程子说专偏不同矣。代言丈曰此以心言。彼以仁言。其义自别。秉远曰仁者心之德则不必以仁与心而分言之。且其为说。诚似有横竖之别。然专偏言大界分在包四与各主。则其曰此心之发者。包举四德而言也。其曰恻隐之发者。直举一端而言也。恐不必二而看也。
仁云云。此专偏言。与程子说专偏不同矣。代言丈曰此以心言。彼以仁言。其义自别。秉远曰仁者心之德则不必以仁与心而分言之。且其为说。诚似有横竖之别。然专偏言大界分在包四与各主。则其曰此心之发者。包举四德而言也。其曰恻隐之发者。直举一端而言也。恐不必二而看也。讲心无出入说。丈席问小注说程子曰。心则无出入。逐物是欲。然则欲者是心外之物耶。盖心只在方寸间。应接事物。无有方所。孔子所谓出入无时者。非真有出入也。特据操舍而言尔。其实心岂有出入。且如人有邪思妄念。即孔子所谓出。而内自点检。皆裁自方寸。计较忖量。则其可谓有出入乎。故程子曰心岂有出入。只据操舍而言。盖言其虽或舍也。而亦非实出耳。代言丈曰孔子之言有出入。是操存舍亡之谓也。程子之言无出入。是出外入内之谓也。执两说而言之。则其意不过曰有存亡而无出入也。秉远曰此段说恐未然。孔子说有。程子说无。意语自别。盖孔子包真妄邪正而直指情状。故谓之有。程子指此心本体而剔出为说。故谓之无。此其所从而言之自不同。故其言曰心岂有出入。只据操舍而言。其意盖曰据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0H 页
 操舍则有出入。据正体则无出入云尔。今欲牵连比并。齐有于无。局出于入。恐非随文解义之道。至于邪思妄念。裁自方寸之说。亦恐未然。从上圣贤。于此心邪妄处。惟恐拒之不严。绝之不牢。故孔子断之曰亡而已。出而已。而程子亦曰逐物是欲。元不曾下一个宽恕之论。今若以此个邪念之计较忖量。同谓之无出入。则是操存时只这样心。舍亡时亦只这样心。其神明不测之妙。何必多让于心得其正时耶。于是座中诸议。群起而攻之。柳丈(玄休),柳子强公晦,姜擎厦。其最力者也。与秉远同者。柳甥(致明)也。
操舍则有出入。据正体则无出入云尔。今欲牵连比并。齐有于无。局出于入。恐非随文解义之道。至于邪思妄念。裁自方寸之说。亦恐未然。从上圣贤。于此心邪妄处。惟恐拒之不严。绝之不牢。故孔子断之曰亡而已。出而已。而程子亦曰逐物是欲。元不曾下一个宽恕之论。今若以此个邪念之计较忖量。同谓之无出入。则是操存时只这样心。舍亡时亦只这样心。其神明不测之妙。何必多让于心得其正时耶。于是座中诸议。群起而攻之。柳丈(玄休),柳子强公晦,姜擎厦。其最力者也。与秉远同者。柳甥(致明)也。二十七日将罢会。诸生开座正厅。丈席出座。言于众曰此地即先生平日讲道之所也。某以旧日门生。获忝堂任。得与诸生复从事于此地。以讲明先生之书。于分诚猥甚。而若因此机会。各自惕念。使此一段事。庶几有所持循。则岂非先生平日所望于后人者。而不佞亦与有荣幸焉。今所讲三说。皆义理头脑。于此苟有见焉。不患不进于高远。而工夫有阶级。意味难镇长。若只随众腾理。作一番胜事而止。则于先生立言垂后之意。其负之矣。此又不佞与诸生之所共勉也。诸生皆起拜教。又曰此堂刱设。盖所以为羹墙寓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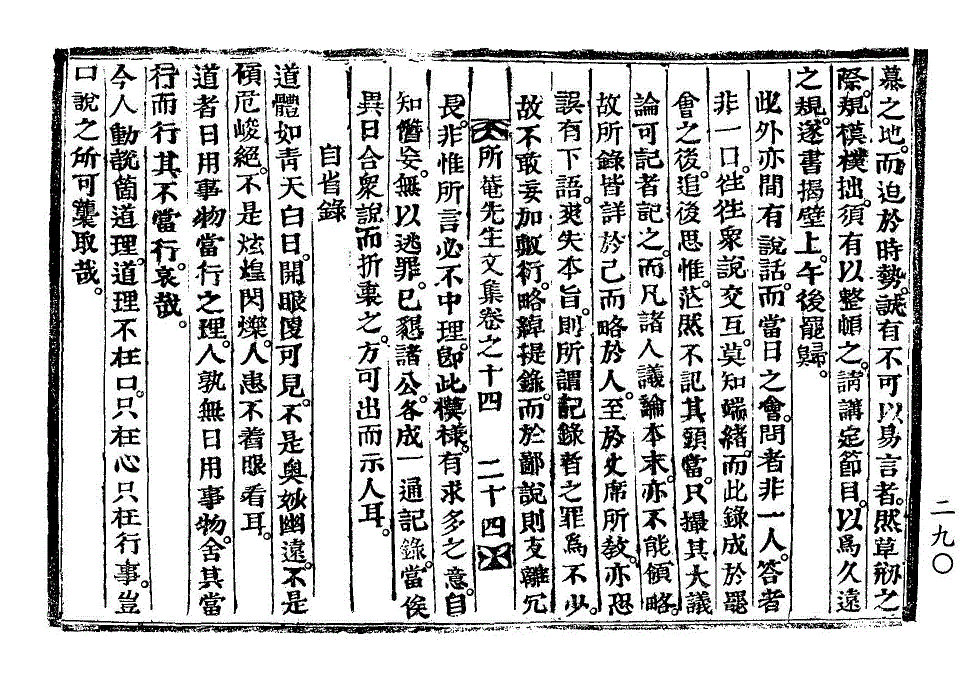 慕之地。而迫于时势。诚有不可以易言者。然草刱之际。规模朴拙。须有以整顿之。请讲定节目。以为久远之规。遂书揭壁上。午后罢归。
慕之地。而迫于时势。诚有不可以易言者。然草刱之际。规模朴拙。须有以整顿之。请讲定节目。以为久远之规。遂书揭壁上。午后罢归。此外亦间有说话。而当日之会。问者非一人。答者非一口。往往众说交互。莫知端绪。此录成于罢会之后。追后思惟。茫然不记其头当。只撮其大议论可记者记之。而凡诸人议论本末。亦不能领略。故所录皆详于己而略于人。至于丈席所教。亦恐误有下语。爽失本旨。则所谓记录者之罪为不少。故不敢妄加敷衍。略绰提录。而于鄙说则支离冗长。非惟所言必不中理。即此模样。有求多之意。自知僭妄。无以逃罪。已恳诸公。各成一通记录。当俟异日合众说而折衷之。方可出而示人耳。
自省录
道体如青天白日。开眼便可见。不是奥妙幽远。不是倾危峻绝。不是炫煌闪烁。人患不着眼看耳。
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人孰无日用事物。舍其当行而行其不当行。哀哉。
今人动说个道理。道理不在口。只在心只在行事。岂口说之所可袭取哉。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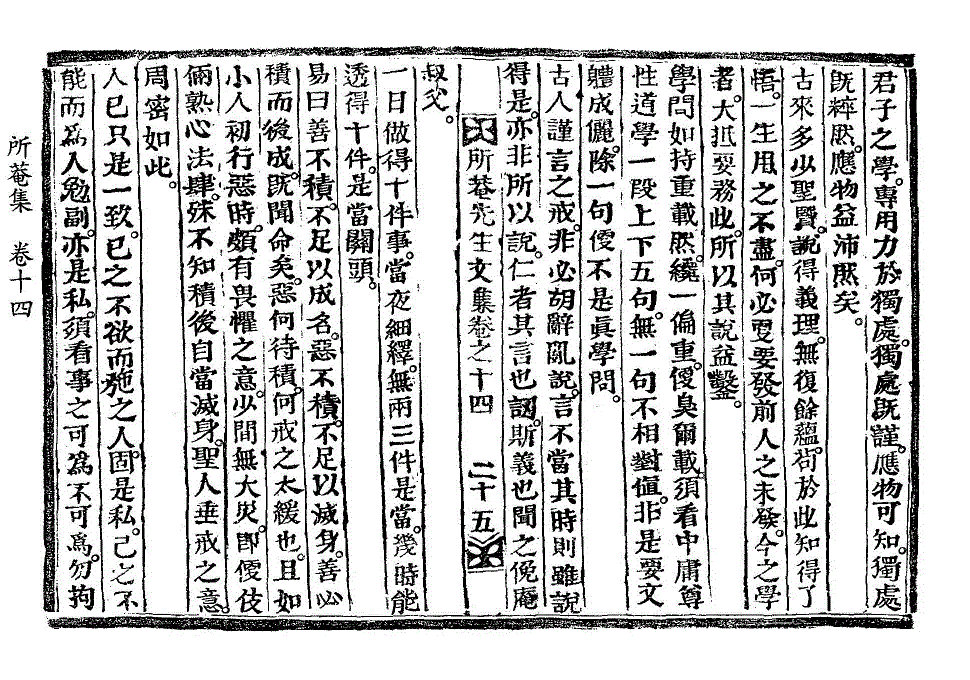 君子之学。专用力于独处。独处既谨。应物可知。独处既粹然。应物益沛然矣。
君子之学。专用力于独处。独处既谨。应物可知。独处既粹然。应物益沛然矣。古来多少圣贤。说得义理。无复馀蕴。苟于此知得了悟。一生用之不尽。何必更要发前人之未发。今之学者。大抵要务此。所以其说益凿。
学问如持重载然。才一偏重。便臭尔载。须看中庸尊性道学一段上下五句。无一句不相对值。非是要文体成俪。除一句便不是真学问。
古人谨言之戒。非必胡辞乱说。言不当其时则虽说得是。亦非所以说。仁者其言也讱。斯义也闻之俛庵叔父。
一日做得十件事。当夜细绎。无两三件是当。几时能透得十件。是当关头。
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善必积而后成。既闻命矣。恶何待积。何戒之太缓也。且如小人初行恶时。颇有畏惧之意。少间无大灾。即便伎俩熟心法肆。殊不知积后自当灭身。圣人垂戒之意。周密如此。
人己只是一致。己之不欲而施之人。固是私。己之不能而为人勉副。亦是私。须看事之可为不可为。勿拘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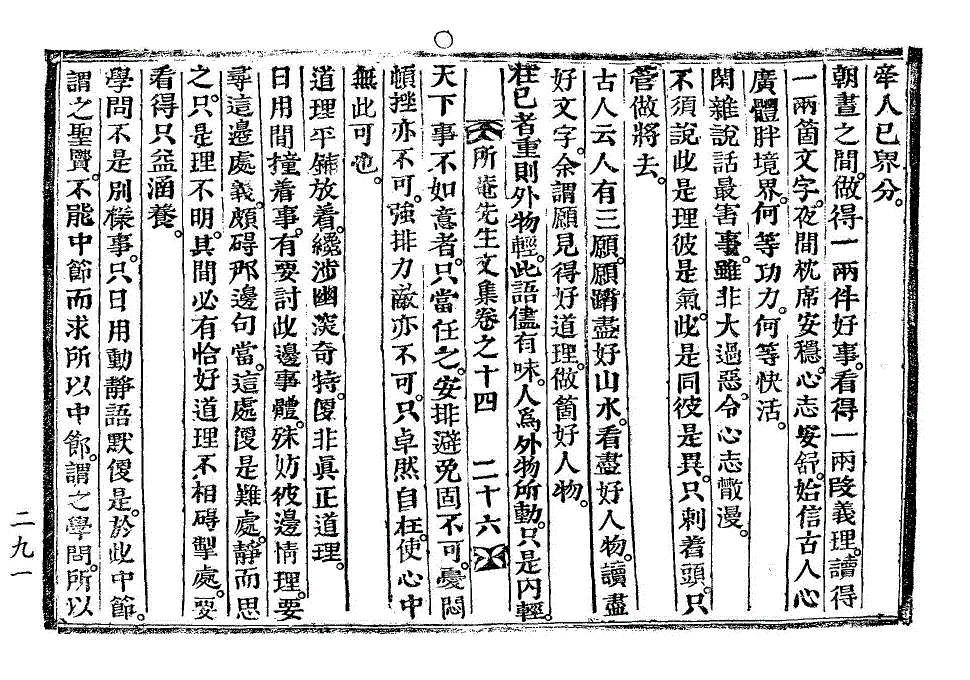 牵人己界分。
牵人己界分。朝昼之间。做得一两件好事。看得一两段义理。读得一两个文字。夜间枕席安稳。心志安舒。始信古人心广体胖境界。何等功力。何等快活。
闲杂说话最害事。虽非大过恶。令心志散漫。
不须说此是理彼是气。此是同彼是异。只刺着头。只管做将去。
古人云人有三愿。愿踏尽好山水。看尽好人物。读尽好文字。余谓愿见得好道理。做个好人物。
在己者重则外物轻。此语尽有味。人为外物所动。只是内轻。
天下事不如意者。只当任之。安排避免固不可。忧闷顿挫亦不可。强排力敌亦不可。只卓然自在。使心中无此可也。
道理平铺放着。才涉幽深奇特。便非真正道理。
日用间撞着事。有要讨此边事体。殊妨彼边情理。要寻这边处义。颇碍那边句当。这处便是难处。静而思之。只是理不明。其间必有恰好道理不相碍掣处。要看得只益涵养。
学问不是别样事。只日用动静语默便是。于此中节。谓之圣贤。不能中节而求所以中节。谓之学问。所以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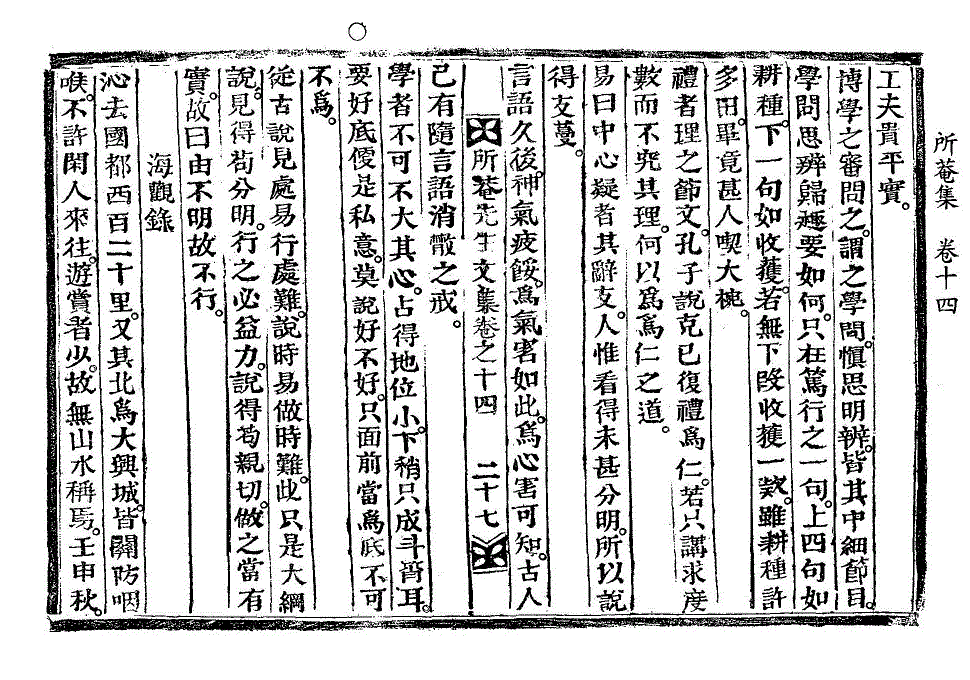 工夫贵平实。
工夫贵平实。博学之审问之。谓之学问。慎思明辨。皆其中细节目。学问思辨归趣要如何。只在笃行之一句。上四句如耕种。下一句如收获。若无下段收获一款。虽耕种许多田。毕竟甚人吃大碗。
礼者理之节文。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若只讲求度数而不究其理。何以为为仁之道。
易曰中心疑者其辞支。人惟看得未甚分明。所以说得支蔓。
言语久后。神气疲馁。为气害如此。为心害可知。古人已有随言语消散之戒。
学者不可不大其心。占得地位小。下稍只成斗筲耳。
要好底便是私意。莫说好不好。只面前当为底不可不为。
从古说见处易行处难。说时易做时难。此只是大纲说。见得苟分明。行之必益力。说得苟亲切。做之当有实。故曰由不明故不行。
海观录
沁去国都西百二十里。又其北为大兴城。皆关防咽喉。不许闲人来往。游赏者少。故无山水称焉。壬申秋。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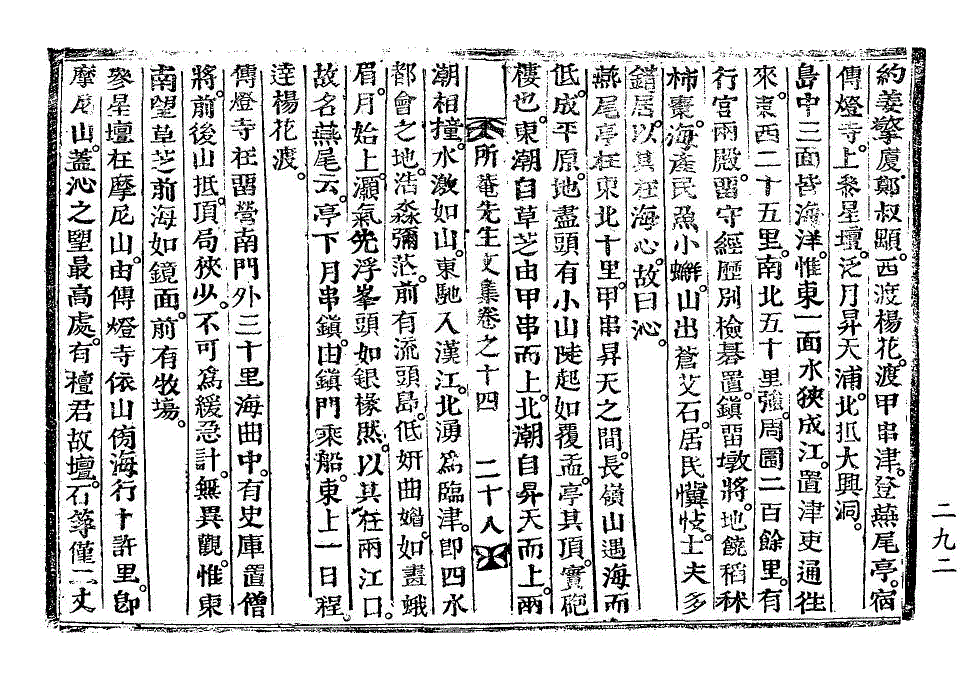 约姜擎厦,郑叔颙。西渡杨花。渡甲串津。登燕尾亭。宿传灯寺。上参星坛。泛月升天浦。北抵大兴洞。
约姜擎厦,郑叔颙。西渡杨花。渡甲串津。登燕尾亭。宿传灯寺。上参星坛。泛月升天浦。北抵大兴洞。岛中三面皆海洋。惟东一面水狭成江。置津吏通往来。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五十里强。周围二百馀里。有行宫两殿。留守经历别检棋置。镇留墩将。地饶稻秫柿枣。海产民鱼小蟹。山出苍艾石。居民懻忮。士夫多错居。以其在海心。故曰沁。
燕尾亭在东北十里。甲串升天之间。长岭山遇海而低。成平原。地尽头有小山陡起如覆盂。亭其顶。实炮楼也。东潮自草芝由甲串而上。北潮自升天而上。两潮相撞。水激如山。东驰入汉江。北涌为临津。即四水都会之地。浩淼弥茫。前有流头岛。低妍曲媚。如画蛾眉。月始上。灏气先浮峰头如银椽然。以其在两江口。故名燕尾云。亭下月串镇。由镇门乘船。东上一日程。达杨花渡。
传灯寺在留营南门外三十里海曲中。有史库置僧将。前后山抵。顶局狭少。不可为缓急计。无异观。惟东南望草芝前海如镜面。前有牧场。
参星坛在摩尼山。由传灯寺依山傍海行十许里。即摩尼山。盖沁之望最高处。有檀君故坛。石筑仅二丈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3H 页
 许。上平容十馀人。前临大海。陡立若飘飘然。东南岛屿错立。如铺豉束戟。西通天际。极望无边。只有瓢子岛微茫如小痣。或曰眼力强者。可卞青齐界。坛下大石离立。有古刻字样。莓苔不可读。盖檀君碑云。
许。上平容十馀人。前临大海。陡立若飘飘然。东南岛屿错立。如铺豉束戟。西通天际。极望无边。只有瓢子岛微茫如小痣。或曰眼力强者。可卞青齐界。坛下大石离立。有古刻字样。莓苔不可读。盖檀君碑云。升天浦。即北津南三十里。沁营北四十里。松营水阔十里。水底皆乱石。波涛日荡。又东自杨花西至天际。旷然成长谷。风势常棼轮。商贾船至此。皆依山成列。如蚁徙然。津头墩台如累棋。由墩台下入舟。恶石如钜齿。最称恶津。朝抵津上候风。夜二更始登舟。风净水稳。俄而月涌上。竟海通白。左右豁然低平。举目爽然。船重行迟。鸡二鸣始泊岸。
大抵山脉从松岳而下。渡升天海为高丽山。东出为留镇为长岭。至燕尾而终。西迤南回。至摩尼而大。皆祖高丽山云。水傍山处。皆陡绝不可拚。无山处皆潮汐所荡。泥泞不得泊。丙子将帅失人。守竟不保。可扼腕也。有古南门遗址。仙源自焚之地。擎厦之先祖亦死焉。有忠烈祠。享十六贤。
由升天镇北抵满月台。古王氏之都。石砌桥梁宛然。东门外有善竹桥。圃隐郑先生死焉。血尚朱殷可认也。东北行十五里。有逝斯亭。花潭隐者别业。又十五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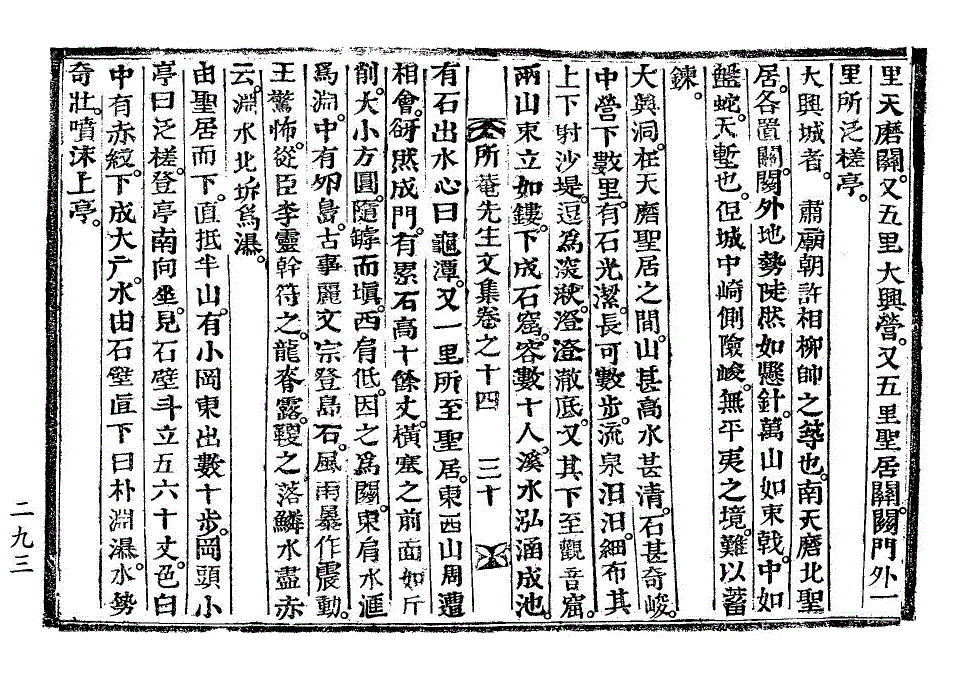 里天磨关。又五里大兴营。又五里圣居关。关门外一里所泛槎亭。
里天磨关。又五里大兴营。又五里圣居关。关门外一里所泛槎亭。大兴城者。 肃庙朝许相柳帅之筑也。南天磨北圣居。各置关。关外地势陡然如悬针。万山如束戟。中如盘蛇。天堑也。但城中崎侧险峻。无平夷之境。难以蓄鍊。
大兴洞。在天磨圣居之间。山甚高水甚清。石甚奇峻。中营下数里。有石光洁。长可数步。流泉汩汩。细布其上下射沙堤。逗为深湫。澄澄澈底。又其下至观音窟。两山束立如镂。下成石窟。容数十人。溪水泓涵成池。有石出水心曰龟潭。又一里所至圣居。东西山周遭相会。谺然成门。有累石高十馀丈。横塞之前面如斤削。大小方圆。随罅而填。西肩低。因之为关。东肩水汇为渊。中有卵岛。古事丽文宗登岛石。风雨㬥作震动。王惊怖。从臣李灵干符之。龙脊露。鞕之落鳞水尽赤云。渊水北坼为瀑。
由圣居而下。直抵半山。有小冈东出数十步。冈头小亭曰泛槎。登亭南向坐。见石壁斗立五六十丈。色白中有赤纹。下成大广。水由石壁直下曰朴渊瀑。水势奇壮。喷沫上亭。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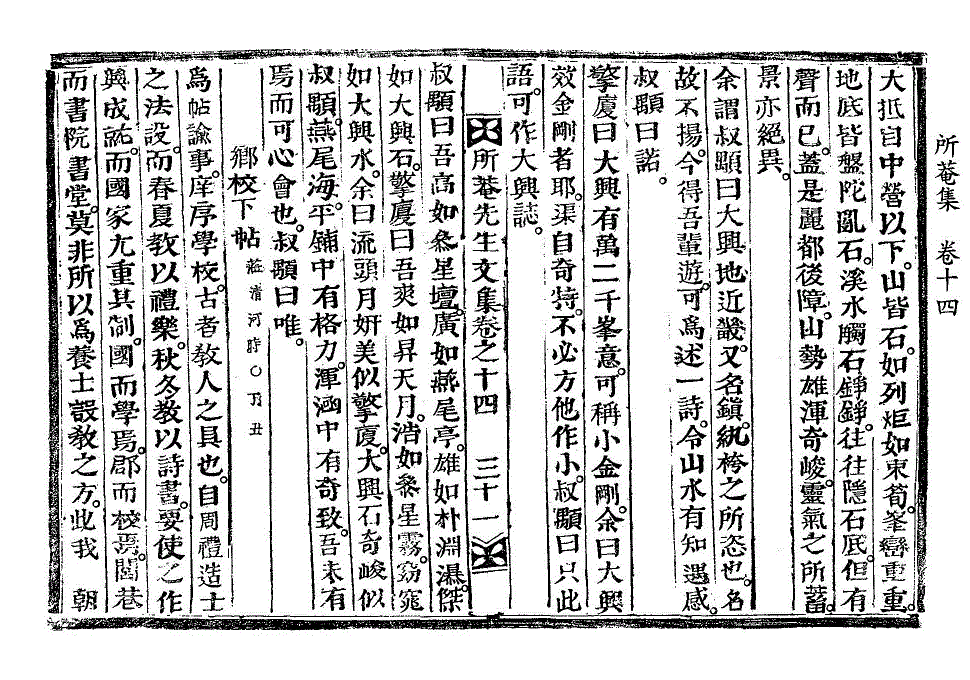 大抵自中营以下。山皆石。如列炬如束笋。峰峦重重。地底皆盘陀乱石。溪水触石铮铮。往往隐石底。但有声而已。盖是丽都后障。山势雄浑奇峻。灵气之所蓄。景亦绝异。
大抵自中营以下。山皆石。如列炬如束笋。峰峦重重。地底皆盘陀乱石。溪水触石铮铮。往往隐石底。但有声而已。盖是丽都后障。山势雄浑奇峻。灵气之所蓄。景亦绝异。余谓叔颙曰大兴地近畿。又名镇。纨裤之所恣也。名故不扬。今得吾辈游。可为述一诗。令山水有知遇感。叔颙曰诺。
擎厦曰大兴有万二千峰意。可称小金刚。余曰大兴效金刚者耶。渠自奇特。不必方他作小。叔颙曰只此语。可作大兴志。
叔颙曰吾高如参星坛。广如燕尾亭。雄如朴渊瀑。杰如大兴石。擎厦曰吾爽如升天月。浩如参星雾。窈窕如大兴水。余曰流头月妍美似擎厦。大兴石奇峻似叔颙。燕尾海。平铺中有格力。浑涵中有奇致。吾未有焉而可心会也。叔颙曰唯。
乡校下帖(莅清河时○丁丑)
为帖谕事。庠序学校。古者教人之具也。自周礼造士之法设。而春夏教以礼乐。秋冬教以诗书。要使之作兴成就。而国家尤重其制。国而学焉。郡而校焉。闾巷而书院书堂。莫非所以为养士设教之方。此我 朝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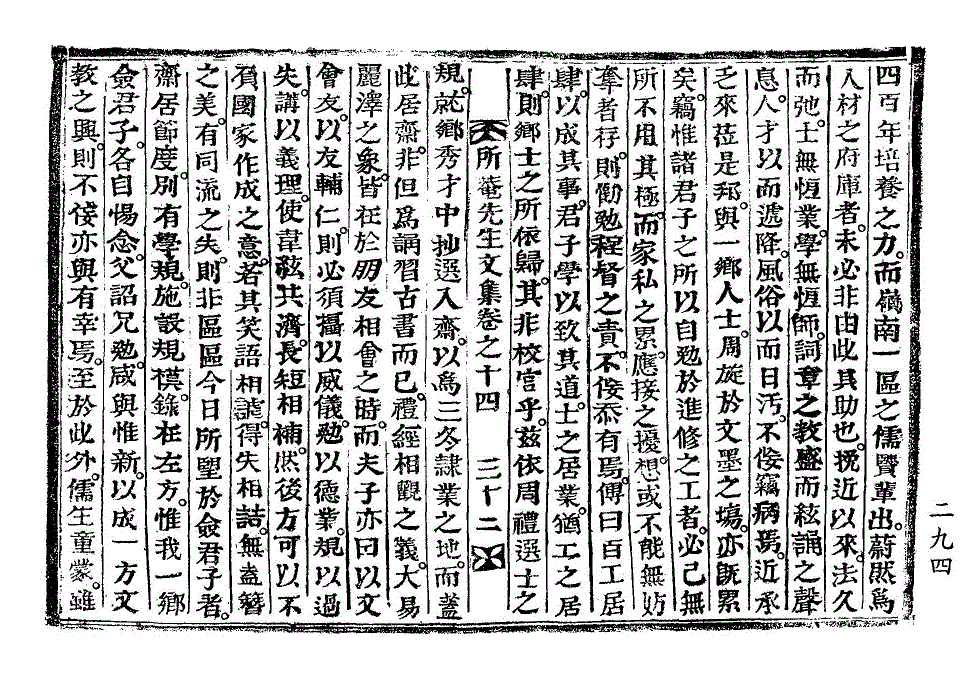 四百年培养之力。而岭南一区之儒贤辈出。蔚然为人材之府库者。未必非由此其助也。挽近以来。法久而弛。士无恒业。学无恒师。词章之教盛而弦诵之声息。人才以而递降。风俗以而日污。不佞窃病焉。近承乏来莅是邦。与一乡人士。周旋于文墨之场。亦既累矣。窃惟诸君子之所以自勉于进修之工者。必已无所不用其极。而家私之累。应接之扰。想或不能无妨夺者存。则劝勉程督之责。不佞忝有焉。传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士之居业。犹工之居肆。则乡士之所依归。其非校宫乎。玆依周礼选士之规。就乡秀才中抄选入斋。以为三冬隶业之地。而盖此居斋。非但为诵习古书而已。礼经相观之义。大易丽泽之象。皆在于朋友相会之时。而夫子亦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则必须摄以威仪。勉以德业。规以过失。讲以义理。使韦弦共济。长短相补。然后方可以不负国家作成之意。若其笑语相谑。得失相诘。无盍簪之美。有同流之失。则非区区今日所望于佥君子者。斋居节度。别有学规。施设规模。录在左方。惟我一乡佥君子。各自惕念。父诏兄勉。咸与惟新。以成一方文教之兴。则不佞亦与有幸焉。至于此外。儒生童蒙。虽
四百年培养之力。而岭南一区之儒贤辈出。蔚然为人材之府库者。未必非由此其助也。挽近以来。法久而弛。士无恒业。学无恒师。词章之教盛而弦诵之声息。人才以而递降。风俗以而日污。不佞窃病焉。近承乏来莅是邦。与一乡人士。周旋于文墨之场。亦既累矣。窃惟诸君子之所以自勉于进修之工者。必已无所不用其极。而家私之累。应接之扰。想或不能无妨夺者存。则劝勉程督之责。不佞忝有焉。传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士之居业。犹工之居肆。则乡士之所依归。其非校宫乎。玆依周礼选士之规。就乡秀才中抄选入斋。以为三冬隶业之地。而盖此居斋。非但为诵习古书而已。礼经相观之义。大易丽泽之象。皆在于朋友相会之时。而夫子亦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则必须摄以威仪。勉以德业。规以过失。讲以义理。使韦弦共济。长短相补。然后方可以不负国家作成之意。若其笑语相谑。得失相诘。无盍簪之美。有同流之失。则非区区今日所望于佥君子者。斋居节度。别有学规。施设规模。录在左方。惟我一乡佥君子。各自惕念。父诏兄勉。咸与惟新。以成一方文教之兴。则不佞亦与有幸焉。至于此外。儒生童蒙。虽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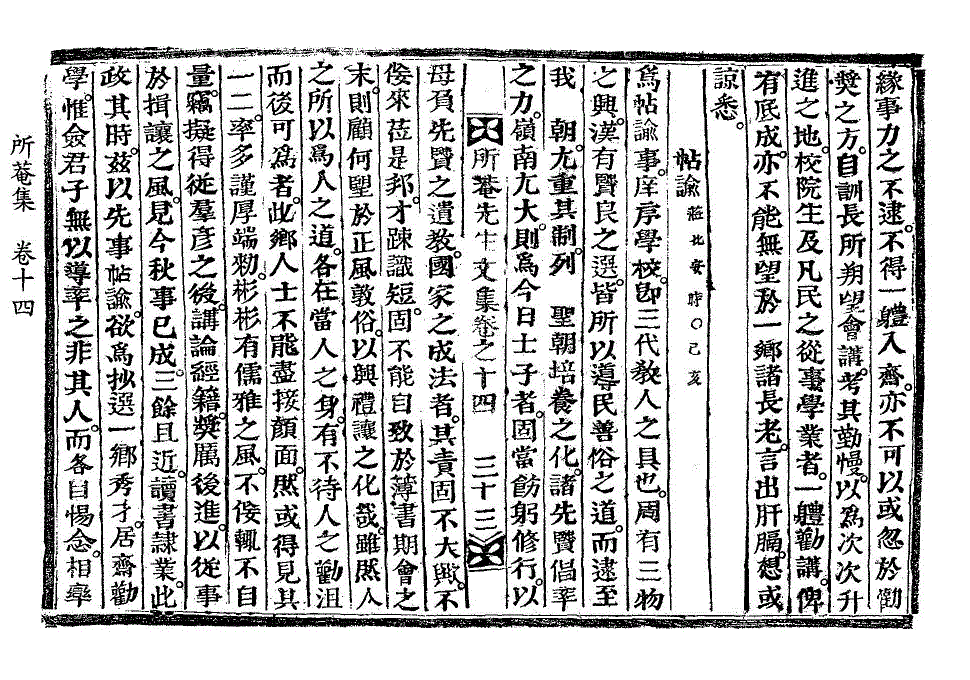 缘事力之不逮。不得一体入斋。亦不可以或忽于劝奖之方。自训长所朔望会讲。考其勤慢。以为次次升进之地。校院生及凡民之从事学业者。一体劝讲。俾有底成。亦不能无望于一乡诸长老。言出肝膈。想或谅悉。
缘事力之不逮。不得一体入斋。亦不可以或忽于劝奖之方。自训长所朔望会讲。考其勤慢。以为次次升进之地。校院生及凡民之从事学业者。一体劝讲。俾有底成。亦不能无望于一乡诸长老。言出肝膈。想或谅悉。帖谕(莅比安时○己亥)
为帖谕事。庠序学校。即三代教人之具也。周有三物之兴。汉有贤良之选。皆所以导民善俗之道。而逮至我 朝。尤重其制。列 圣朝培养之化。诸先贤倡率之力。岭南尤大。则为今日士子者。固当饬躬修行。以毋负先贤之遗教。国家之成法者。其责固不大欤。不佞来莅是邦。才疏识短。固不能自致于簿书期会之末。则顾何望于正风敦俗。以兴礼让之化哉。虽然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有不待人之劝沮而后可为者。此乡人士不能尽接颜面。然或得见其一二。率多谨厚端敕。彬彬有儒雅之风。不佞辄不自量。窃拟得从群彦之后。讲论经籍。奖厉后进。以从事于揖让之风。见今秋事已成。三馀且近。读书隶业。此政其时。玆以先事帖谕。欲为抄选一乡秀才。居斋劝学。惟佥君子无以导率之非其人。而各自惕念。相率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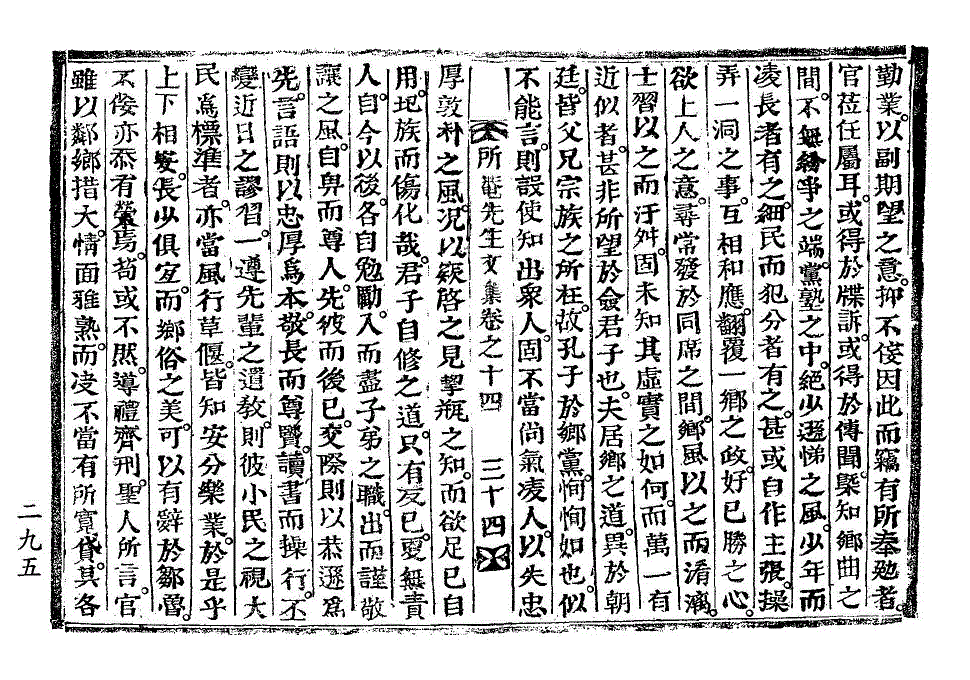 勤业。以副期望之意。抑不佞因此而窃有所奉勉者。官莅任属耳。或得于牒诉。或得于传闻。槩知乡曲之间。不无纷争之端。党塾之中。绝少逊悌之风。少年而凌长者有之。细民而犯分者有之。甚或自作主张。操弄一洞之事。互相和应。翻覆一乡之政。好己胜之心。欲上人之意。寻常发于同席之间。乡风以之而淆漓。士习以之而污舛。固未知其虚实之如何。而万一有近似者。甚非所望于佥君子也。夫居乡之道。异于朝廷。皆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则设使知出众人。固不当尚气凌人。以失忠厚敦朴之风。况以窾启之见挈瓶之知。而欲足己自用。圮族而伤化哉。君子自修之道。只有反己。更无责人。自今以后。各自勉励。入而尽子弟之职。出而谨敬让之风。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交际则以恭逊为先。言语则以忠厚为本。敬长而尊贤。读书而操行。丕变近日之谬习。一遵先辈之遗教。则彼小民之视大民为标准者。亦当风行草偃。皆知安分乐业。于是乎上下相安。长少俱宜。而乡俗之美。可以有辞于邹鲁。不佞亦忝有荣焉。苟或不然。导礼齐刑。圣人所言。官虽以邻乡措大。情面雅熟。而决不当有所宽贷。其各
勤业。以副期望之意。抑不佞因此而窃有所奉勉者。官莅任属耳。或得于牒诉。或得于传闻。槩知乡曲之间。不无纷争之端。党塾之中。绝少逊悌之风。少年而凌长者有之。细民而犯分者有之。甚或自作主张。操弄一洞之事。互相和应。翻覆一乡之政。好己胜之心。欲上人之意。寻常发于同席之间。乡风以之而淆漓。士习以之而污舛。固未知其虚实之如何。而万一有近似者。甚非所望于佥君子也。夫居乡之道。异于朝廷。皆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则设使知出众人。固不当尚气凌人。以失忠厚敦朴之风。况以窾启之见挈瓶之知。而欲足己自用。圮族而伤化哉。君子自修之道。只有反己。更无责人。自今以后。各自勉励。入而尽子弟之职。出而谨敬让之风。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交际则以恭逊为先。言语则以忠厚为本。敬长而尊贤。读书而操行。丕变近日之谬习。一遵先辈之遗教。则彼小民之视大民为标准者。亦当风行草偃。皆知安分乐业。于是乎上下相安。长少俱宜。而乡俗之美。可以有辞于邹鲁。不佞亦忝有荣焉。苟或不然。导礼齐刑。圣人所言。官虽以邻乡措大。情面雅熟。而决不当有所宽贷。其各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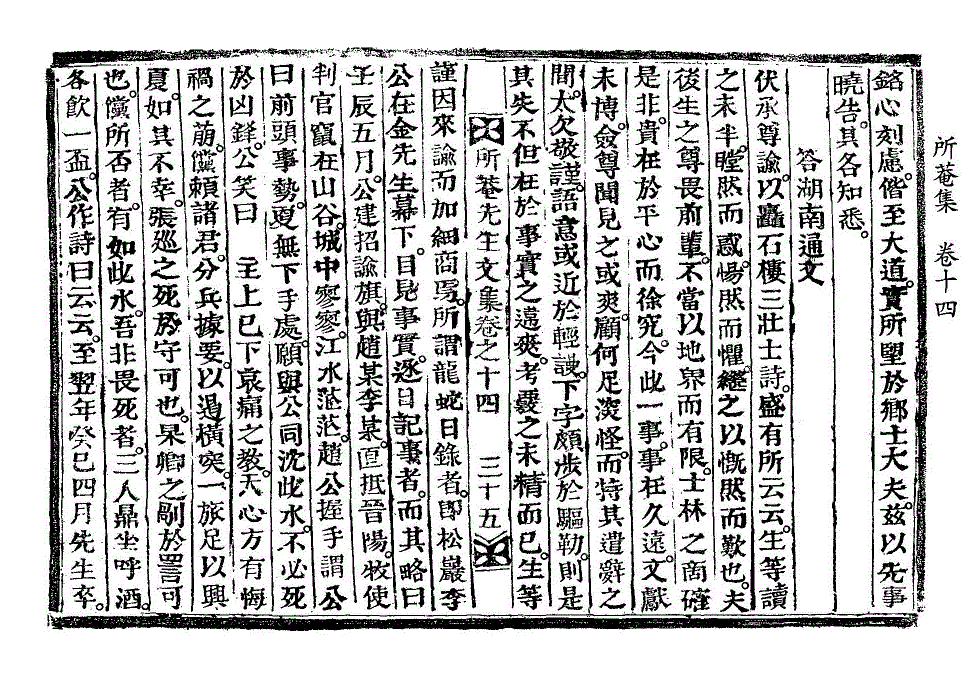 铭心刻虑。偕至大道。实所望于乡士大夫。玆以先事晓告。其各知悉。
铭心刻虑。偕至大道。实所望于乡士大夫。玆以先事晓告。其各知悉。答湖南通文
伏承尊谕。以矗石楼三壮士诗。盛有所云云。生等读之未半。瞠然而惑。惕然而惧。继之以慨然而叹也。夫后生之尊畏前辈。不当以地界而有限。士林之商确是非。贵在于平心而徐究。今此一事。事在久远。文献未博。佥尊闻见之或爽。顾何足深怪。而特其遣辞之间。太欠敬谨。语意或近于轻谩。下字颇涉于驱勒。则是其失不但在于事实之违爽。考覈之未精而已。生等谨因来谕而加细商焉。所谓龙蛇日录者。即松岩李公在金先生幕下。目见事实。逐日记事者。而其略曰壬辰五月。公建招谕旗。与赵某李某。直抵晋阳。牧使判官窜在山谷。城中寥寥。江水茫茫。赵公握手谓公曰前头事势。更无下手处。愿与公同沈此水。不必死于凶锋。公笑曰 主上已下哀痛之教。天心方有悔祸之萌。傥赖诸君。分兵据要。以遏横突。一旅足以兴夏。如其不幸。张巡之死于守可也。杲卿之剐于詈可也。傥所否者。有如此水。吾非畏死者。三人鼎坐呼酒。各饮一杯。公作诗曰云云。至翌年癸巳四月先生卒。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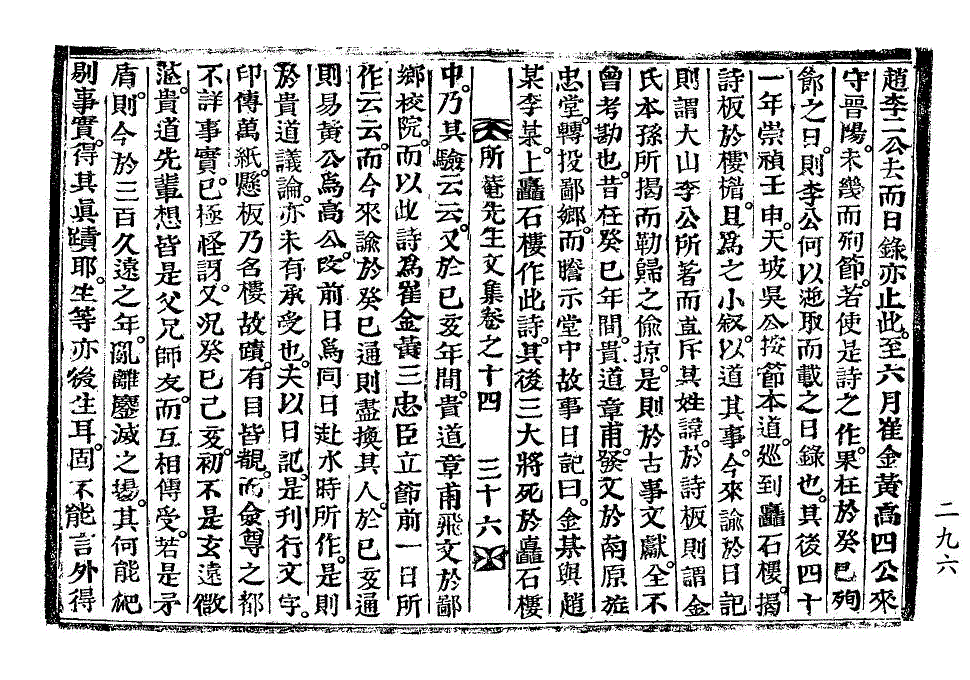 赵李二公去而日录亦止此。至六月崔金黄高四公来守晋阳。未几而殉节。若使是诗之作。果在于癸巳殉节之日。则李公何以逆取而载之日录也。其后四十一年崇祯壬申。天坡昊公按节本道。巡到矗石楼。揭诗板于楼楣。且为之小叙。以道其事。今来谕于日记则谓大山李公所著而直斥其姓讳。于诗板则谓金氏本孙所揭而勒归之偷掠。是则于古事文献。全不曾考勘也。昔在癸巳年间。贵道章甫。发文于南原㫌忠堂。转投鄙乡。而誊示堂中故事日记曰。金某与赵某李某。上矗石楼作此诗。其后三大将死于矗石楼中。乃其验云云。又于己亥年间。贵道章甫飞文于鄙乡校院。而以此诗为崔金黄三忠臣立节前一日所作云云。而今来谕于癸巳通则尽换其人。于己亥通则易黄公为高公。改前日为同日赴水时所作。是则于贵道议论。亦未有承受也。夫以日记。是刊行文字。印传万纸。悬板乃名楼故迹。有目皆睹。而佥尊之都不详事实。已极怪讶。又况癸巳己亥。初不是玄远微茫。贵道先辈想皆是父兄师友。而互相传受。若是矛盾。则今于三百久远之年。乱离鏖灭之场。其何能爬剔事实。得其真迹耶。生等亦后生耳。固不能言外得
赵李二公去而日录亦止此。至六月崔金黄高四公来守晋阳。未几而殉节。若使是诗之作。果在于癸巳殉节之日。则李公何以逆取而载之日录也。其后四十一年崇祯壬申。天坡昊公按节本道。巡到矗石楼。揭诗板于楼楣。且为之小叙。以道其事。今来谕于日记则谓大山李公所著而直斥其姓讳。于诗板则谓金氏本孙所揭而勒归之偷掠。是则于古事文献。全不曾考勘也。昔在癸巳年间。贵道章甫。发文于南原㫌忠堂。转投鄙乡。而誊示堂中故事日记曰。金某与赵某李某。上矗石楼作此诗。其后三大将死于矗石楼中。乃其验云云。又于己亥年间。贵道章甫飞文于鄙乡校院。而以此诗为崔金黄三忠臣立节前一日所作云云。而今来谕于癸巳通则尽换其人。于己亥通则易黄公为高公。改前日为同日赴水时所作。是则于贵道议论。亦未有承受也。夫以日记。是刊行文字。印传万纸。悬板乃名楼故迹。有目皆睹。而佥尊之都不详事实。已极怪讶。又况癸巳己亥。初不是玄远微茫。贵道先辈想皆是父兄师友。而互相传受。若是矛盾。则今于三百久远之年。乱离鏖灭之场。其何能爬剔事实。得其真迹耶。生等亦后生耳。固不能言外得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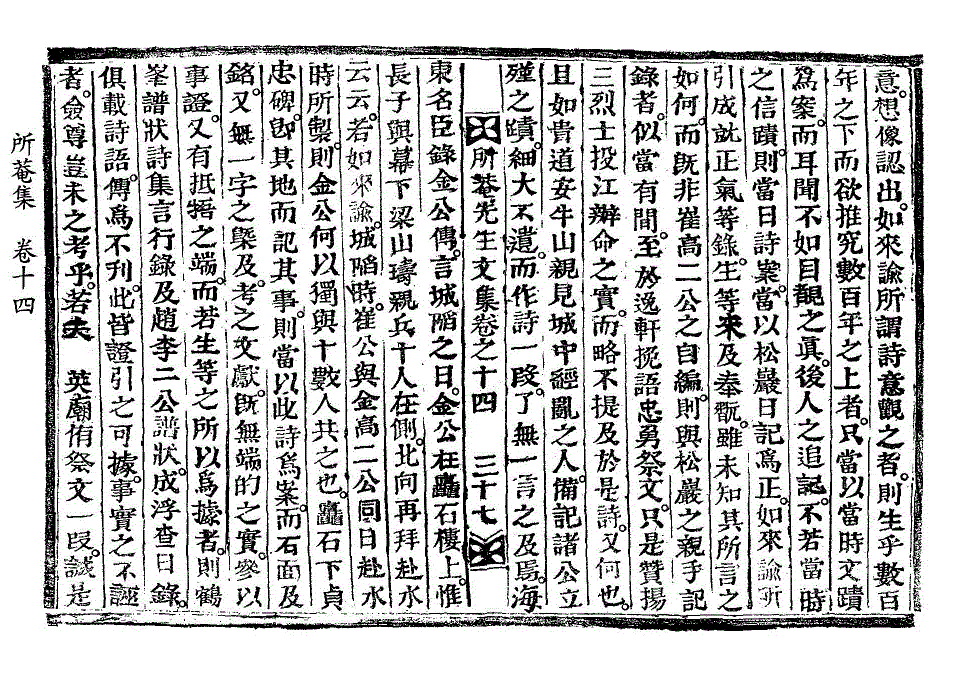 意。想像认出。如来谕所谓诗意观之者。则生乎数百年之下而欲推究数百年之上者。只当以当时文迹为案。而耳闻不如目睹之真。后人之追记。不若当时之信迹。则当日诗案。当以松岩日记为正。如来谕所引成就正气等录。生等未及奉玩。虽未知其所言之如何。而既非崔高二公之自编。则与松岩之亲手记录者。似当有间。至于逸轩挽语忠勇祭文。只是赞扬三烈士投江办命之实。而略不提及于是诗。又何也。且如贵道安牛山亲见城中经乱之人。备记诸公立殣之迹。细大不遗。而作诗一段。了无一言之及焉。海东名臣录金公传。言城陷之日。金公在矗石楼上。惟长子与幕下梁山璹亲兵十人在侧。北向再拜赴水云云。若如来谕。城陷时。崔公与金高二公同日赴水时所制。则金公何以独与十数人共之也。矗石下贞忠碑。即其地而记其事。则当以此诗为案。而石面及铭。又无一字之槩及。考之文献。既无端的之实。参以事證。又有抵牾之端。而若生等之所以为据者。则鹤峰谱状诗集言行录及赵李二公谱状。成浮查日录。俱载诗语。传为不刊。此皆證引之可据。事实之不诬者。佥尊岂未之考乎。若夫 英庙侑祭文一段。诚是
意。想像认出。如来谕所谓诗意观之者。则生乎数百年之下而欲推究数百年之上者。只当以当时文迹为案。而耳闻不如目睹之真。后人之追记。不若当时之信迹。则当日诗案。当以松岩日记为正。如来谕所引成就正气等录。生等未及奉玩。虽未知其所言之如何。而既非崔高二公之自编。则与松岩之亲手记录者。似当有间。至于逸轩挽语忠勇祭文。只是赞扬三烈士投江办命之实。而略不提及于是诗。又何也。且如贵道安牛山亲见城中经乱之人。备记诸公立殣之迹。细大不遗。而作诗一段。了无一言之及焉。海东名臣录金公传。言城陷之日。金公在矗石楼上。惟长子与幕下梁山璹亲兵十人在侧。北向再拜赴水云云。若如来谕。城陷时。崔公与金高二公同日赴水时所制。则金公何以独与十数人共之也。矗石下贞忠碑。即其地而记其事。则当以此诗为案。而石面及铭。又无一字之槩及。考之文献。既无端的之实。参以事證。又有抵牾之端。而若生等之所以为据者。则鹤峰谱状诗集言行录及赵李二公谱状。成浮查日录。俱载诗语。传为不刊。此皆證引之可据。事实之不诬者。佥尊岂未之考乎。若夫 英庙侑祭文一段。诚是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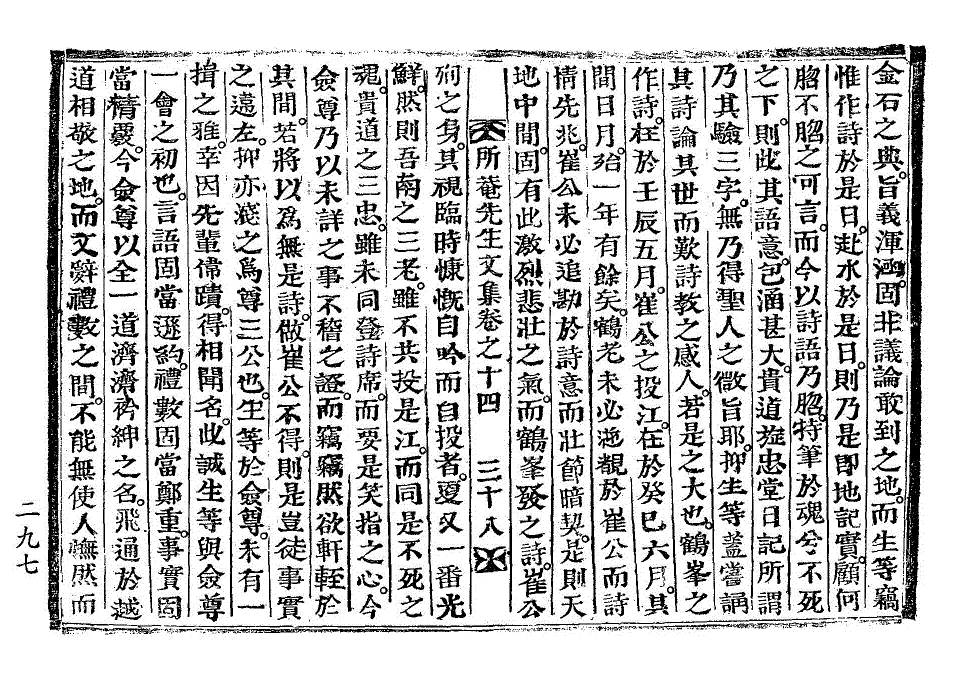 金石之典。旨义浑涵。固非议论敢到之地。而生等窃惟作诗于是日。赴水于是日。则乃是即地记实。顾何吻不吻之可言。而今以诗语乃吻。特笔于魂兮不死之下。则此其语意。包涵甚大。贵道㫌忠堂日记所谓乃其验三字。无乃得圣人之微旨耶。抑生等盖尝诵其诗论其世而叹诗教之感人。若是之大也。鹤峰之作诗。在于壬辰五月。崔公之投江。在于癸巳六月。其间日月。殆一年有馀矣。鹤老未必逆睹于崔公而诗情先兆。崔公未必追勘于诗意而壮节暗契。是则天地中间。固有此激烈悲壮之气。而鹤峰发之诗。崔公殉之身。其视临时慷慨自吟而自投者。更又一番光鲜。然则吾南之三老。虽不共投是江。而同是不死之魂。贵道之三忠。虽未同登诗席。而要是笑指之心。今佥尊乃以未详之事不稽之證。而窃窃然欲轩轾于其间。若将以为无是诗。做崔公不得。则是岂徒事实之违左。抑亦浅之为尊三公也。生等于佥尊。未有一揖之雅。幸因先辈伟迹。得相闻名。此诚生等与佥尊一会之初也。言语固当逊约。礼数固当郑重。事实固当精覈。今佥尊以全一道济济衿绅之名。飞通于越道相敬之地。而文辞礼数之间。不能无使人怃然而
金石之典。旨义浑涵。固非议论敢到之地。而生等窃惟作诗于是日。赴水于是日。则乃是即地记实。顾何吻不吻之可言。而今以诗语乃吻。特笔于魂兮不死之下。则此其语意。包涵甚大。贵道㫌忠堂日记所谓乃其验三字。无乃得圣人之微旨耶。抑生等盖尝诵其诗论其世而叹诗教之感人。若是之大也。鹤峰之作诗。在于壬辰五月。崔公之投江。在于癸巳六月。其间日月。殆一年有馀矣。鹤老未必逆睹于崔公而诗情先兆。崔公未必追勘于诗意而壮节暗契。是则天地中间。固有此激烈悲壮之气。而鹤峰发之诗。崔公殉之身。其视临时慷慨自吟而自投者。更又一番光鲜。然则吾南之三老。虽不共投是江。而同是不死之魂。贵道之三忠。虽未同登诗席。而要是笑指之心。今佥尊乃以未详之事不稽之證。而窃窃然欲轩轾于其间。若将以为无是诗。做崔公不得。则是岂徒事实之违左。抑亦浅之为尊三公也。生等于佥尊。未有一揖之雅。幸因先辈伟迹。得相闻名。此诚生等与佥尊一会之初也。言语固当逊约。礼数固当郑重。事实固当精覈。今佥尊以全一道济济衿绅之名。飞通于越道相敬之地。而文辞礼数之间。不能无使人怃然而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298H 页
 失图者。则如生等何足说。或有以窥贵道之浅深则岂小故耶。不直则道不见。是以敢言之及此。伏惟有以谅察幸甚。
失图者。则如生等何足说。或有以窥贵道之浅深则岂小故耶。不直则道不见。是以敢言之及此。伏惟有以谅察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