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x 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杂著
杂著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399H 页
 心出入集说(壬申)
心出入集说(壬申)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朱子曰孔子言心。操之则在此。舍之则失去。其出入无定时。亦无定处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 按心无形迹。操之者非如以手而捉物也。舍之者非如以手而弃物也。程子所谓敬以直内。这便是操之之道。而其舍之者。恒由于不敬也。盖此一心。神明不测。非存则亡。不出则入。无一时而非此心时节。无一处而非此心处所。夫焉有一定之时。又焉有一定之处哉。是以自非圣贤以上。得失之无常易。保守之不舍难。为心学者可不戒哉。
朱子曰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佗分明道出入无时。且看自家今汩汩没没在这里。非出入而何。 按众人之心。胶胶挠挠。静帖之时少。飞扬之时多。虽得暂息。旋又欻起。头出头没。不可捉摸。以言其出入。不亦宜乎。非专以汩汩没没。谓之出入也。
朱子曰孟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只是状人之心是个难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则是在这里。出则是亡失了。此大约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论心之本体也。 按有形之物。固可以把持之易。无形之物。安得以硬捉不动。所谓操之者。不过如秉彝之秉执中之执耳。所谓舍之者。亦如坐忘坐驰之云耳。是以出入便是操存舍亡之谓也。入而不昧者。本心之正也。出而无节者。客心之邪也。然而以体用对出入则体为入而用为出。此所以谓大约言之者也。出入者心之机也。非所以状本体之虚灵也。亦非专指他放逸者而为言也。其贯始终该真妄者。于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3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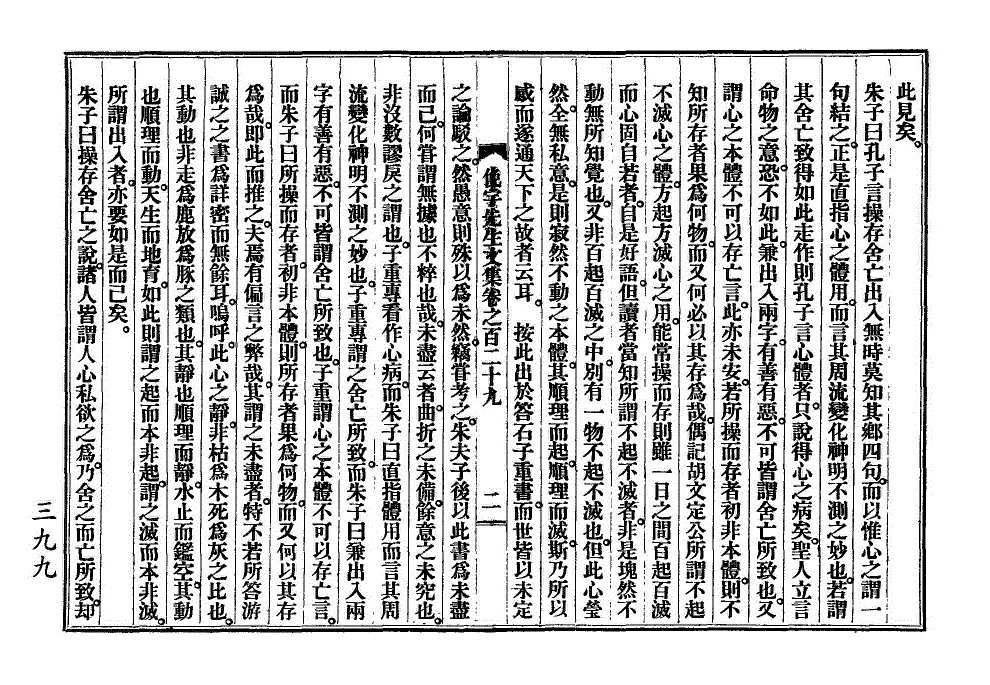 此见矣。
此见矣。朱子曰孔子言操存舍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四句。而以惟心之谓一句结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若谓其舍亡致得如此走作则孔子言心体者。只说得心之病矣。圣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亡所致也。又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不知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为哉。偶记胡文定公所谓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则虽一日之间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语。但读者当知所谓不起不灭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又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但此心莹然。全无私意。是则寂然不动之本体。其顺理而起。顺理而灭。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 按此出于答石子重书。而世皆以未定之论驳之。然愚意则殊以为未然。窃尝考之。朱夫子后以此书为未尽而已。何尝谓无据也不粹也哉。未尽云者。曲折之未备。馀意之未究也。非没数谬戾之谓也。子重专看作心病。而朱子曰直指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子重专谓之舍亡所致。而朱子曰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亡所致也。子重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而朱子曰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以其存为哉。即此而推之。夫焉有偏言之弊哉。其谓之未尽者。特不若所答游诚之之书为详密而无馀耳。呜呼。此心之静。非枯为木死为灰之比也。其动也非走为鹿放为豚之类也。其静也顺理而静。水止而鉴空。其动也顺理而动。天生而地育。如此则谓之起而本非起。谓之灭而本非灭。所谓出入者。亦要如是而已矣。
朱子曰操存舍亡之说。诸人皆谓人心私欲之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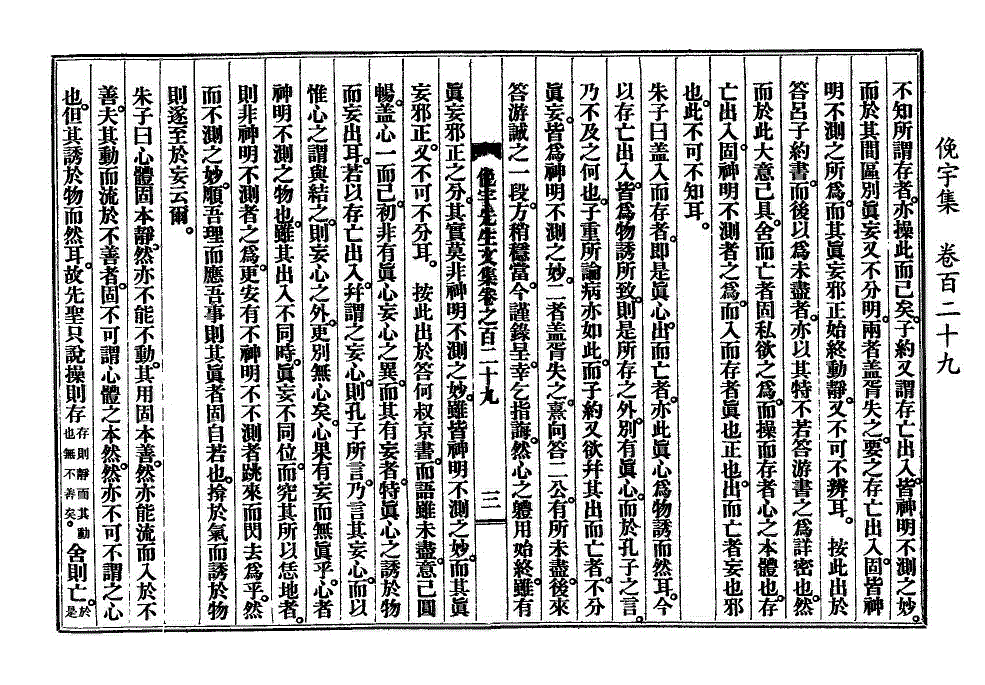 不知所谓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约又谓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测之妙。而于其间区别真妄又不分明。两者盖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测之所为。而其真妄邪正始终动静。又不可不辨耳。 按此出于答吕子约书。而后以为未尽者。亦以其特不若答游书之为详密也。然而于此大意已具。舍而亡者固私欲之为。而操而存者心之本体也。存亡出入。固神明不测者之为。而入而存者真也正也。出而亡者妄也邪也。此不可不知耳。
不知所谓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约又谓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测之妙。而于其间区别真妄又不分明。两者盖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测之所为。而其真妄邪正始终动静。又不可不辨耳。 按此出于答吕子约书。而后以为未尽者。亦以其特不若答游书之为详密也。然而于此大意已具。舍而亡者固私欲之为。而操而存者心之本体也。存亡出入。固神明不测者之为。而入而存者真也正也。出而亡者妄也邪也。此不可不知耳。朱子曰盖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为物诱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为物诱所致。则是所存之外。别有真心。而于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也。子重所论病亦如此。而子约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为神明不测之妙。二者盖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尽。后来答游诚之一段。方稍稳当。今谨录呈。幸乞指诲。然心之体用始终。虽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实莫非神明不测之妙。虽皆神明不测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 按此出于答何叔京书。而语虽未尽。意已圆畅。盖心一而已。初非有真心妄心之异。而其有妄者。特真心之诱于物而妄出耳。若以存亡出入。并谓之妄心。则孔子所言。乃言其妄心。而以惟心之谓与结之。则妄心之外。更别无心矣。心果有妄而无真乎。心者神明不测之物也。虽其出入不同时。真妄不同位。而究其所以恁地者。则非神明不测者之为。更安有不神明不不测者跳来而闪去为乎。然而不测之妙。顺吾理而应吾事则其真者固自若也。掩于气而诱于物则遂至于妄云尔。
朱子曰心体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动。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动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谓心体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谓之心也。但其诱于物而然耳。故先圣只说操则存(存则静而其动也无不善矣。)舍则亡。(于是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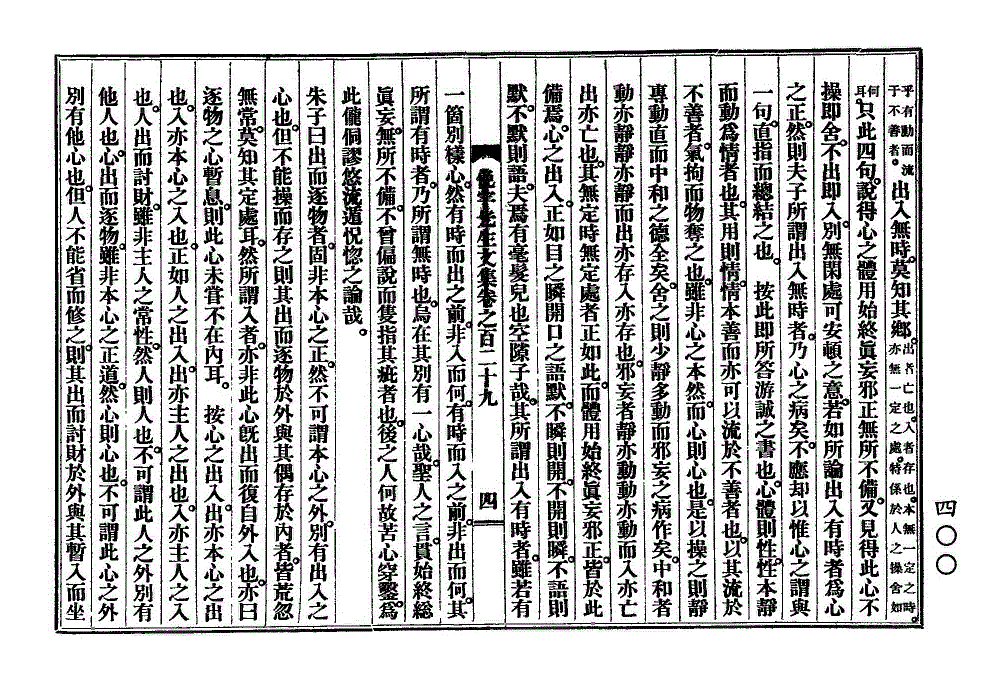 乎有动而流于不善者。)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时。亦无一定之处。特系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说得心之体用始终真妄邪正无所不备。又见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闲处可安顿之意。若如所论出入有时者为心之正。然则夫子所谓出入无时者。乃心之病矣。不应却以惟心之谓与一句。直指而总结之也。 按此即所答游诚之书也。心体则性。性本静而动为情者也。其用则情。情本善而亦可以流于不善者也。以其流于不善者。气拘而物夺之也。虽非心之本然。而心则心也。是以操之则静专动直而中和之德全矣。舍之则少静多动而邪妄之病作矣。中和者动亦静静亦静而出亦存入亦存也。邪妄者静亦动动亦动而入亦亡出亦亡也。其无定时无定处者正如此。而体用始终真妄邪正。皆于此备焉。心之出入。正如目之瞬开口之语默。不瞬则开。不开则瞬。不语则默。不默则语。夫焉有毫发儿也空隙子哉。其所谓出入有时者。虽若有一个别样心。然有时而出之前。非入而何。有时而入之前。非出而何。其所谓有时者。乃所谓无时也。乌在其别有一心哉。圣人之言。贯始终总真妄。无所不备。不曾偏说而只指其疵者也。后之人何故苦心穿凿。为此儱侗谬悠流遁恍惚之论哉。
乎有动而流于不善者。)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时。亦无一定之处。特系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说得心之体用始终真妄邪正无所不备。又见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闲处可安顿之意。若如所论出入有时者为心之正。然则夫子所谓出入无时者。乃心之病矣。不应却以惟心之谓与一句。直指而总结之也。 按此即所答游诚之书也。心体则性。性本静而动为情者也。其用则情。情本善而亦可以流于不善者也。以其流于不善者。气拘而物夺之也。虽非心之本然。而心则心也。是以操之则静专动直而中和之德全矣。舍之则少静多动而邪妄之病作矣。中和者动亦静静亦静而出亦存入亦存也。邪妄者静亦动动亦动而入亦亡出亦亡也。其无定时无定处者正如此。而体用始终真妄邪正。皆于此备焉。心之出入。正如目之瞬开口之语默。不瞬则开。不开则瞬。不语则默。不默则语。夫焉有毫发儿也空隙子哉。其所谓出入有时者。虽若有一个别样心。然有时而出之前。非入而何。有时而入之前。非出而何。其所谓有时者。乃所谓无时也。乌在其别有一心哉。圣人之言。贯始终总真妄。无所不备。不曾偏说而只指其疵者也。后之人何故苦心穿凿。为此儱侗谬悠流遁恍惚之论哉。朱子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谓本心之外。别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则其出而逐物于外与其偶存于内者。皆荒忽无常。莫知其定处耳。然所谓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复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暂息。则此心未尝不在内耳。 按心之出入。出亦本心之出也。入亦本心之入也。正如人之出入。出亦主人之出也。入亦主人之入也。人出而讨财。虽非主人之常性。然人则人也。不可谓此人之外别有他人也。心出而逐物。虽非本心之正道。然心则心也。不可谓此心之外别有他心也。但人不能省而修之。则其出而讨财于外与其暂入而坐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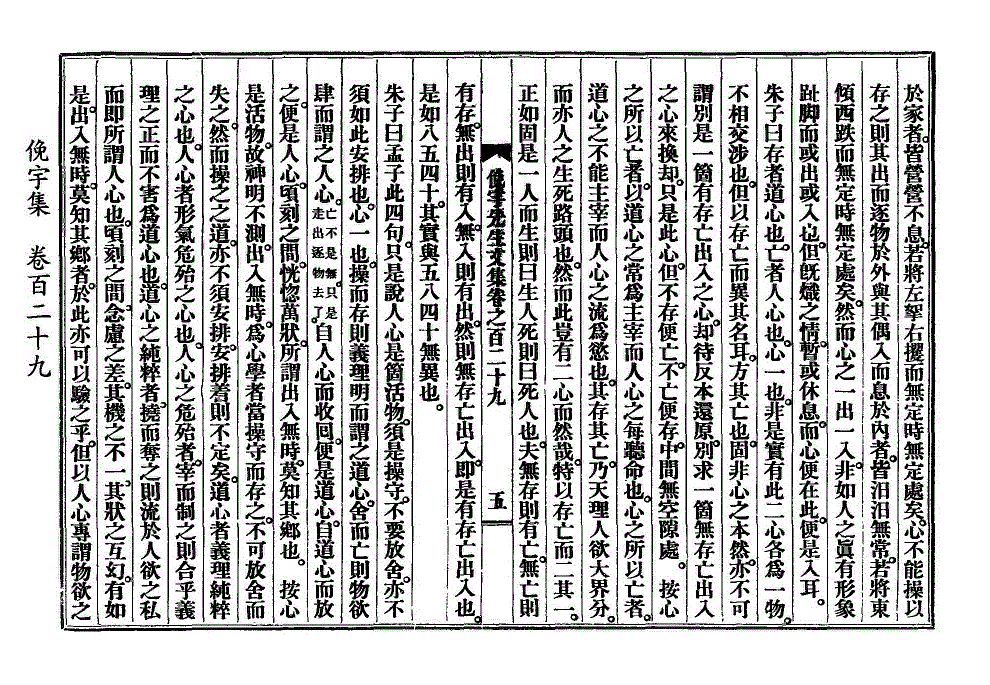 于家者。皆营营不息。若将左挐右攫而无定时无定处矣。心不能操以存之则其出而逐物于外与其偶入而息于内者。皆汩汩无常。若将东倾西跌而无定时无定处矣。然而心之一出一入。非如人之真有形象趾脚而或出或入也。但既炽之情。暂或休息。而心便在此。便是入耳。
于家者。皆营营不息。若将左挐右攫而无定时无定处矣。心不能操以存之则其出而逐物于外与其偶入而息于内者。皆汩汩无常。若将东倾西跌而无定时无定处矣。然而心之一出一入。非如人之真有形象趾脚而或出或入也。但既炽之情。暂或休息。而心便在此。便是入耳。朱子曰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实有此二心各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异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谓别是一个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还原。别求一个无存亡出入之心来换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间无空隙处。 按心之所以亡者。以道心之常为主宰而人心之每听命也。心之所以亡(一作存)者。道心之不能主宰而人心之流为欲也。其存其亡。乃天理人欲大界分。而亦人之生死路头也。然而此岂有二心而然哉。特以存亡而二其一。正如固是一人而生则曰生人死则曰死人也。夫无存则有亡。无亡则有存。无出则有入。无入则有出。然则无存亡出入。即是有存亡出入也。是如八五四十。其实与五八四十无异也。
朱子曰孟子此四句。只是说人心是个活物。须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须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则义理明而谓之道心。舍而亡则物欲肆而谓之人心。(亡不是无。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顷刻之间。恍惚万状。所谓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也。 按心是活物。故神明不测。出入无时。为心学者当操守而存之。不可放舍而失之。然而操之之道。亦不须安排。安排着则不定矣。道心者义理纯粹之心也。人心者形气危殆之心也。人心之危殆者。宰而制之则合乎义理之正而不害为道心也。道心之纯粹者。挠而夺之则流于人欲之私而即所谓人心也。顷刻之间。念虑之差。其机之不一。其状之互幻。有如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于此亦可以验之乎。但以人心专谓物欲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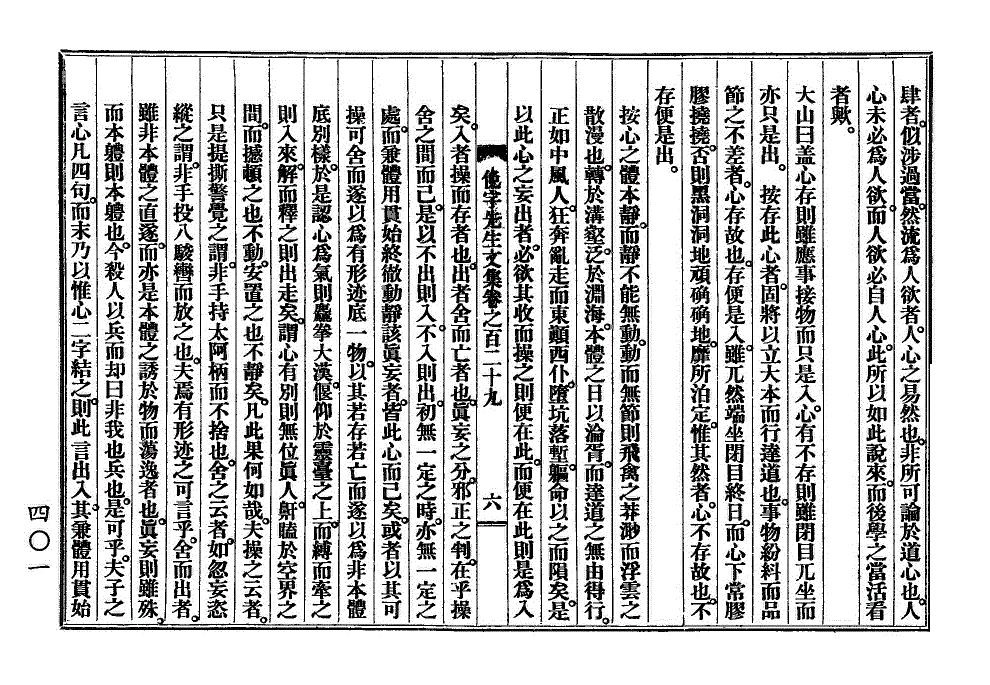 肆者。似涉过当。然流为人欲者。人心之易然也。非所可论于道心也。人心未必为人欲。而人欲必自人心。此所以如此说来。而后学之当活看者欤。
肆者。似涉过当。然流为人欲者。人心之易然也。非所可论于道心也。人心未必为人欲。而人欲必自人心。此所以如此说来。而后学之当活看者欤。大山曰盖心存则虽应事接物而只是入。心有不存则虽闭目兀坐而亦只是出。 按存此心者。固将以立大本而行达道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之不差者。心存故也。存便是入。虽兀然端坐闭目终日。而心下常胶胶挠挠。否则黑洞洞地顽确确地。靡所泊定。惟其然者。心不存故也。不存便是出。
按心之体本静。而静不能无动。动而无节则飞禽之莽渺而浮云之散漫也。转于沟壑。泛于渊海。本体之日以沦胥。而达道之无由得行。正如中风人。狂奔乱走而东颠西仆。堕坑落堑。躯命以之而陨矣。是以此心之妄出者。必欲其收而操之则便在此。而便在此则是为入矣。入者操而存者也。出者舍而亡者也。真妄之分。邪正之判。在乎操舍之间而已。是以不出则入。不入则出。初无一定之时。亦无一定之处。而兼体用贯始终彻动静该真妄者。皆此心而已矣。或者以其可操可舍而遂以为有形迹底一物。以其若存若亡而遂以为非本体底别样。于是认心为气则粗拳大汉。偃仰于灵台之上。而缚而牵之则入来。解而释之则出走矣。谓心有别则无位真人。鼾瞌于空界之间。而撼顿之也不动。安置之也不静矣。凡此果何如哉。夫操之云者。只是提撕警觉之谓。非手持太阿柄而不舍也。舍之云者。如忽妄恣纵之谓。非手投八骏辔而放之也。夫焉有形迹之可言乎。舍而出者。虽非本体之直遂。而亦是本体之诱于物而荡逸者也。真妄则虽殊。而本体则本体也。今杀人以兵而却曰非我也兵也。是可乎。夫子之言心凡四句。而末乃以惟心二字结之。则此言出入。其兼体用贯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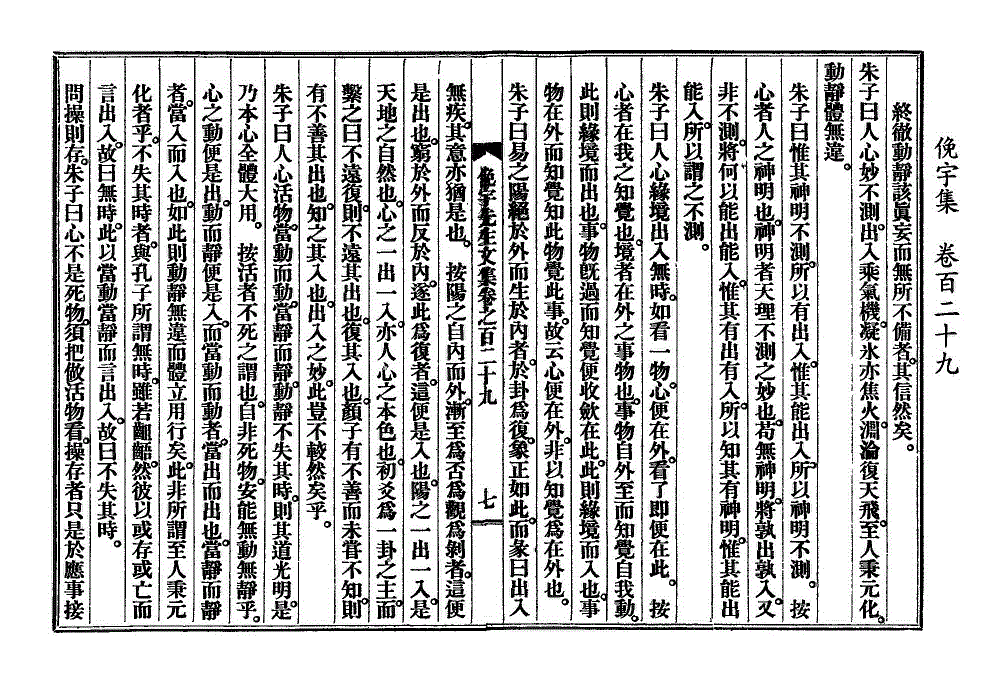 终彻动静该真妄而无所不备者。其信然矣。
终彻动静该真妄而无所不备者。其信然矣。朱子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凝冰亦焦火。渊沦复天飞。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
朱子曰惟其神明不测。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测。 按心者人之神明也。神明者天理不测之妙也。苟无神明。将孰出孰入。又非不测。将何以能出能入。惟其有出有入。所以知其有神明。惟其能出能入。所以谓之不测。
朱子曰人心缘境出入无时。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 按心者在我之知觉也。境者在外之事物也。事物自外至而知觉自我动。此则缘境而出也。事物既过而知觉便收敛在此。此则缘境而入也。事物在外而知觉知此物觉此事。故云心便在外。非以知觉为在外也。
朱子曰易之阳绝于外而生于内者。于卦为复。象正如此。而彖曰出入无疾。其意亦犹是也。 按阳之自内而外。渐至为否为观为剥者。这便是出也。穷于外而反于内。遂此为复者。这便是入也。阳之一出一入。是天地之自然也。心之一出一入。亦人心之本色也。初爻为一卦之主。而系之曰不远复。则不远其出也。复其入也。颜子有不善而未尝不知。则有不善其出也。知之其入也。出入之妙。此岂不较然矣乎。
朱子曰人心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体大用。 按活者不死之谓也。自非死物。安能无动无静乎。心之动便是出。动而静便是入。而当动而动者。当出而出也。当静而静者。当入而入也。如此则动静无违而体立用行矣。此非所谓至人秉元化者乎。不失其时者。与孔子所谓无时。虽若龃龉。然彼以或存或亡而言出入。故曰无时。此以当动当静而言出入。故曰不失其时。
问操则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须把做活物看。操存者只是于应事接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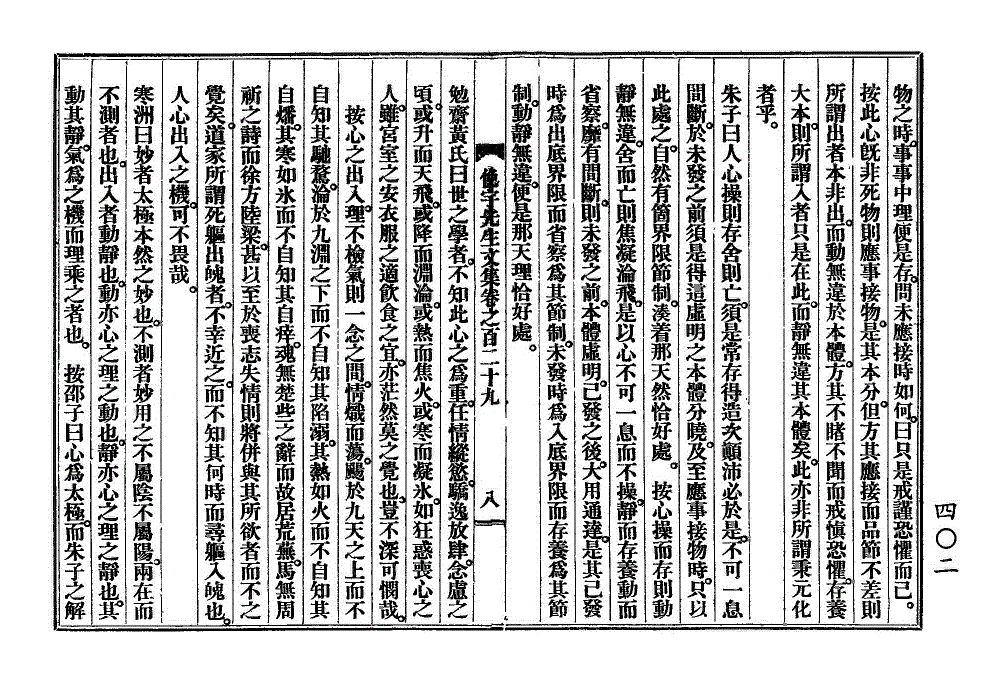 物之时。事事中理便是存。问未应接时如何。曰只是戒谨恐惧而已。 按此心既非死物则应事接物。是其本分。但方其应接而品节不差则所谓出者本非出。而动无违于本体。方其不睹不闻而戒慎恐惧。存养大本。则所谓入者只是在此。而静无违其本体矣。此亦非所谓秉元化者乎。
物之时。事事中理便是存。问未应接时如何。曰只是戒谨恐惧而已。 按此心既非死物则应事接物。是其本分。但方其应接而品节不差则所谓出者本非出。而动无违于本体。方其不睹不闻而戒慎恐惧。存养大本。则所谓入者只是在此。而静无违其本体矣。此亦非所谓秉元化者乎。朱子曰人心操则存舍则亡。须是常存得造次颠沛必于是。不可一息问断。于未发之前须是得这虚明之本体分晓。及至应事接物时。只以此处之。自然有个界限节制。凑着那天然恰好处。 按心操而存则动静无违。舍而亡则焦凝沦飞。是以心不可一息而不操。静而存养动而省察。靡有间断。则未发之前。本体虚明。已发之后。大用通达。是其已发时为出底界限而省察为其节制。未发时为入底界限而存养为其节制。动静无违。便是那天理恰好处。
勉斋黄氏曰世之学者。不知此心之为重。任情纵欲。骄逸放肆。念虑之顷。或升而天飞。或降而渊沦。或热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丧心之人。虽宫室之安衣服之适饮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觉也。岂不深可悯哉。 按心之出入。理不检气则一念之间。情炽而荡。飏于九天之上而不自知其驰骛。沦于九渊之下而不自知其陷溺。其热如火而不自知其自燔。其寒如冰而不自知其自㾕。魂无楚些之辞而故居荒芜。马无周祈之诗而徐方陆梁。甚以至于丧志失情则将并与其所欲者而不之觉矣。道家所谓死躯出魄者。不幸近之。而不知其何时而寻躯入魄也。人心出入之机。可不畏哉。
寒洲曰妙者太极本然之妙也。不测者妙用之不属阴不属阳。两在而不测者也。出入者动静也。动亦心之理之动也。静亦心之理之静也。其动其静。气为之机而理乘之者也。 按邵子曰心为太极。而朱子之解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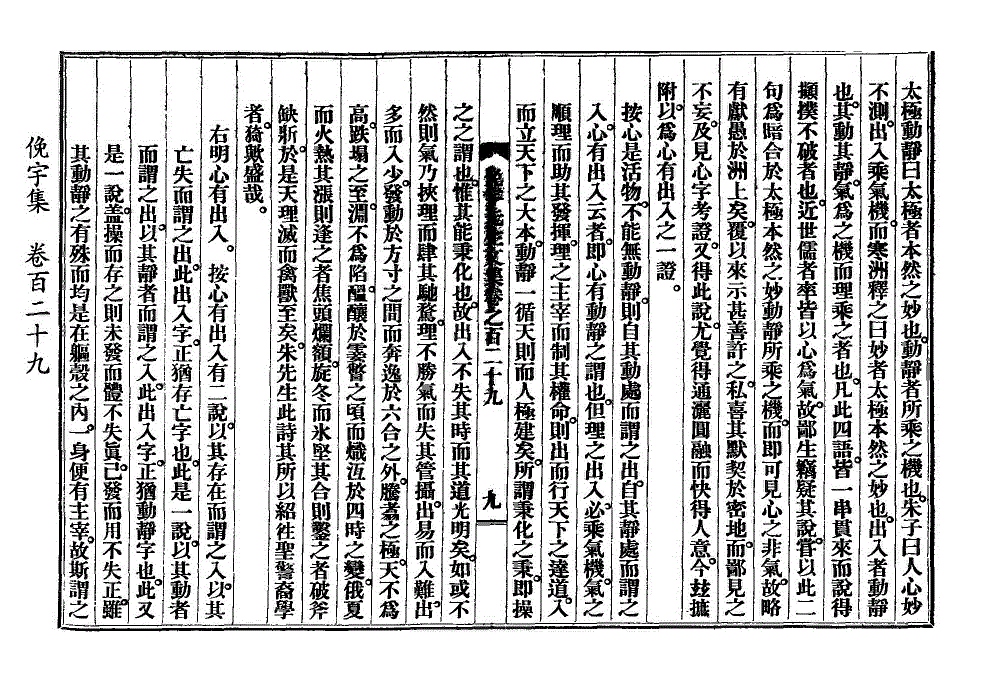 太极动静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朱子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而寒洲释之曰妙者太极本然之妙也。出入者动静也。其动其静。气为之机而理乘之者也。凡此四语。皆一串贯来而说得攧扑不破者也。近世儒者率皆以心为气。故鄙生窃疑其说。尝以此二句为暗合于太极本然之妙动静所乘之机。而即可见心之非气。故略有献愚于洲上矣。覆以来示甚善许之。私喜其默契于密地。而鄙见之不妄。及见心字考證。又得此说。尤觉得通洒圆融而快得人意。今玆摭附。以为心有出入之一證。
太极动静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朱子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而寒洲释之曰妙者太极本然之妙也。出入者动静也。其动其静。气为之机而理乘之者也。凡此四语。皆一串贯来而说得攧扑不破者也。近世儒者率皆以心为气。故鄙生窃疑其说。尝以此二句为暗合于太极本然之妙动静所乘之机。而即可见心之非气。故略有献愚于洲上矣。覆以来示甚善许之。私喜其默契于密地。而鄙见之不妄。及见心字考證。又得此说。尤觉得通洒圆融而快得人意。今玆摭附。以为心有出入之一證。按心是活物。不能无动静。则自其动处而谓之出。自其静处而谓之入。心有出入云者。即心有动静之谓也。但理之出入。必乘气机。气之顺理而助其发挥。理之主宰而制其权命。则出而行天下之达道。入而立天下之大本。动静一循天则而人极建矣。所谓秉化之秉。即操之之谓也。惟其能秉化也。故出入不失其时而其道光明矣。如或不然则气乃挟理而肆其驰骛。理不胜气而失其管摄。出易而入难。出多而入少。发动于方寸之间而奔逸于六合之外。腾翥之极。天不为高。跌塌之至。渊不为陷。酝酿于霎瞥之顷而炽冱于四时之变。俄夏而火热其涨则逢之者焦头烂额。旋冬而冰坚其合则凿之者破斧缺斨。于是天理灭而禽兽至矣。朱先生此诗其所以绍往圣警裔学者。猗欤盛哉。
右明心有出入。 按心有出入有二说。以其存在而谓之入。以其亡失而谓之出。此出入字。正犹存亡字也。此是一说。以其动者而谓之出。以其静者而谓之入。此出入字。正犹动静字也。此又是一说。盖操而存之则未发而体不失真。已发而用不失正。虽其动静之有殊而均是在躯壳之内。一身便有主宰。故斯谓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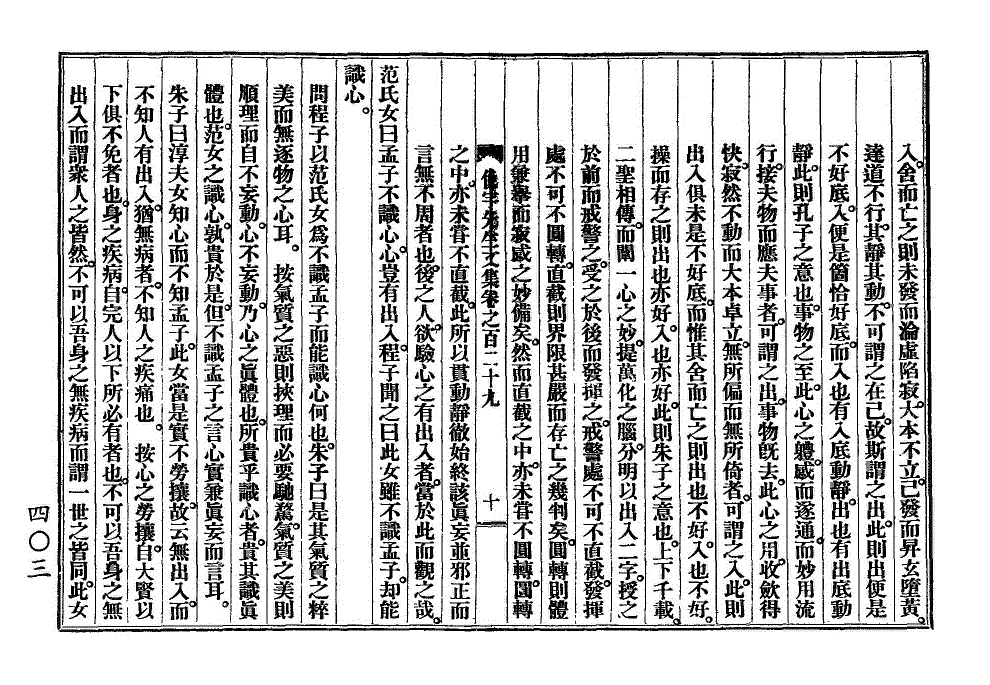 入。舍而亡之则未发而沦虚陷寂。大本不立。已发而升玄堕黄。达道不行。其静其动。不可谓之在己。故斯谓之出。此则出便是不好底。入便是个恰好底。而入也有入底动静。出也有出底动静。此则孔子之意也。事物之至。此心之体。感而遂通。而妙用流行。接夫物而应夫事者。可谓之出。事物既去。此心之用。收敛得快。寂然不动而大本卓立。无所偏而无所倚者。可谓之入。此则出入俱未是不好底。而惟其舍而亡之则出也不好。入也不好。操而存之则出也亦好。入也亦好。此则朱子之意也。上下千载。二圣相传。而阐一心之妙。提万化之脑。分明以出入二字。授之于前而戒警之。受之于后而发挥之。戒警处不可不直截。发挥处不可不圆转。直截则界限甚严而存亡之几判矣。圆转则体用兼举而寂感之妙备矣。然而直截之中。亦未尝不圆转。圆转之中。亦未尝不直截。此所以贯动静彻始终该真妄并邪正而言无不周者也。后之人。欲验心之有出入者。当于此而观之哉。
入。舍而亡之则未发而沦虚陷寂。大本不立。已发而升玄堕黄。达道不行。其静其动。不可谓之在己。故斯谓之出。此则出便是不好底。入便是个恰好底。而入也有入底动静。出也有出底动静。此则孔子之意也。事物之至。此心之体。感而遂通。而妙用流行。接夫物而应夫事者。可谓之出。事物既去。此心之用。收敛得快。寂然不动而大本卓立。无所偏而无所倚者。可谓之入。此则出入俱未是不好底。而惟其舍而亡之则出也不好。入也不好。操而存之则出也亦好。入也亦好。此则朱子之意也。上下千载。二圣相传。而阐一心之妙。提万化之脑。分明以出入二字。授之于前而戒警之。受之于后而发挥之。戒警处不可不直截。发挥处不可不圆转。直截则界限甚严而存亡之几判矣。圆转则体用兼举而寂感之妙备矣。然而直截之中。亦未尝不圆转。圆转之中。亦未尝不直截。此所以贯动静彻始终该真妄并邪正而言无不周者也。后之人。欲验心之有出入者。当于此而观之哉。范氏女曰孟子不识心。心岂有出入。程子闻之曰此女虽不识孟子。却能识心。
问程子以范氏女为不识孟子而能识心何也。朱子曰是其气质之粹美而无逐物之心耳。 按气质之恶则挟理而必要驰骛。气质之美则顺理而自不妄动。心不妄动。乃心之真体也。所贵乎识心者。贵其识真体也。范女之识心。孰贵于是。但不识孟子之言心实兼真妄而言耳。
朱子曰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当是实不劳攘。故云无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犹无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按心之劳攘。自大贤以下俱不免者也。身之疾病。自完人以下所必有者也。不可以吾身之无出入而谓众人之皆然。不可以吾身之无疾病而谓一世之皆同。此女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4H 页
 之言心。其自知则明矣。而他人有心则全不能忖度。盖其有大贤之气质。而无大贤之许多知觉耳。
之言心。其自知则明矣。而他人有心则全不能忖度。盖其有大贤之气质。而无大贤之许多知觉耳。朱子曰想此女子自觉得个它心尝湛然无出入故如此说。 按吾心湛然。别无出入。故执此而为说。然却不知才出门外。举世为汩汩然也。此所以谓之自觉者乎。
朱子曰有人言无出入说得是好。某看来只是它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动走作。所以自不见得有出入。要之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于佗一身。不可为众人言。众人是有出入。圣贤立教。通为众人言。不为一人言。 按言心之无出入者。只验其自心之无出入也。心无出入则曷非好事。但众人之生。受气不齐。昏明强弱清浊美恶。或顺理而守之成之。或掩理而颠之倒之。心之有出入。众人之所同也。心之无出入。一人之所独也。以我所独。自知则得矣。而谓人己若则不知人者也。圣人之教。正所以为天下万世许多人之心有出入者而欲其操而存之。使之无出入也。非所以为一人之心无出入者。而欲其舍而亡之。使之有出入也。
大山曰范氏女见心体湛然。全无劳攘。故云无出入。 按湛然心体。卓然不倚。无逐物而出之时。亦无撇物而入之时。则其心诚好矣。其言无出入亦固矣。范氏之女其知心乎。
按心兼理气。气逆则理微。心统性情。情炽则性凿。众人之心。理不检气。情不遂性。流动走作之时多。存主静贴之时少。一念之间。出入靡常。此孟子所以引夫子之言而垂戒众人。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而要必无流动走作之失者也。范氏女见此心之湛然。遂以为心无出入。虽不识众人之心不与我同。而圣人之言。统戒众人。然其于本体之湛然则诚有实见得及者。故程夫子以识心许之也。盖此女气合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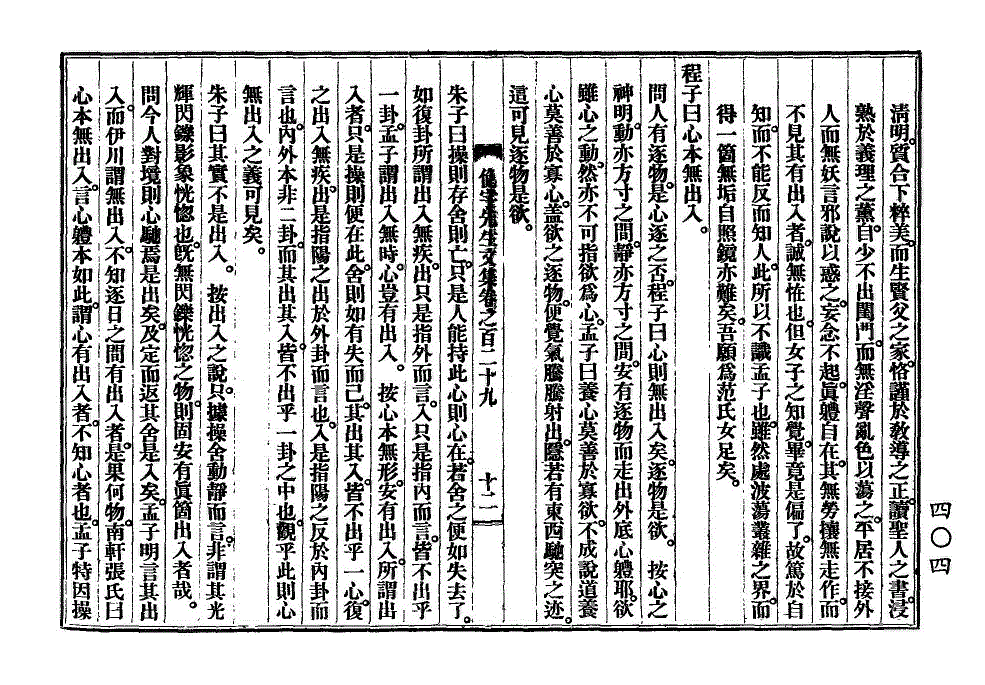 清明。质合下粹美。而生贤父之家。恪谨于教导之正。读圣人之书。浸熟于义理之薰。自少不出闺门。而无淫声乱色以荡之。平居不接外人而无妖言邪说以惑之。妄念不起。真体自在。其无劳攘无走作。而不见其有出入者。诚无怪也。但女子之知觉。毕竟是偏了。故笃于自知。而不能反而知人。此所以不识孟子也。虽然处波荡丛杂之界。而得一个无垢自照镜亦难矣。吾愿为范氏女足矣。
清明。质合下粹美。而生贤父之家。恪谨于教导之正。读圣人之书。浸熟于义理之薰。自少不出闺门。而无淫声乱色以荡之。平居不接外人而无妖言邪说以惑之。妄念不起。真体自在。其无劳攘无走作。而不见其有出入者。诚无怪也。但女子之知觉。毕竟是偏了。故笃于自知。而不能反而知人。此所以不识孟子也。虽然处波荡丛杂之界。而得一个无垢自照镜亦难矣。吾愿为范氏女足矣。程子曰心本无出入。
问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程子曰心则无出入矣。逐物是欲。 按心之神明。动亦方寸之间。静亦方寸之间。安有逐物而走出外底心体耶。欲虽心之动。然亦不可指欲为心。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成说道养心莫善于寡心。盖欲之逐物。便觉气腾腾射出。隐若有东西驰突之迹。这可见逐物是欲。
朱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则心在。若舍之便如失去了。如复卦所谓出入无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内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谓出入无时。心岂有出入。 按心本无形。安有出入。所谓出入者。只是操则便在此。舍则如有失而已。其出其入。皆不出乎一心。复之出入无疾。出是指阳之出于外卦而言也。入是指阳之反于内卦而言也。内外本非二卦。而其出其入。皆不出乎一卦之中也。观乎此则心无出入之义可见矣。
朱子曰其实不是出入。 按出入之说。只据操舍动静而言。非谓其光辉闪铄影象恍惚也。既无闪铄恍惚之物。则固安有真个出入者哉。
问今人对境则心驰焉是出矣。及定而返其舍是入矣。孟子明言其出入。而伊川谓无出入。不知逐日之间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南轩张氏曰心本无出入。言心体本如此。谓心有出入者。不知心者也。孟子特因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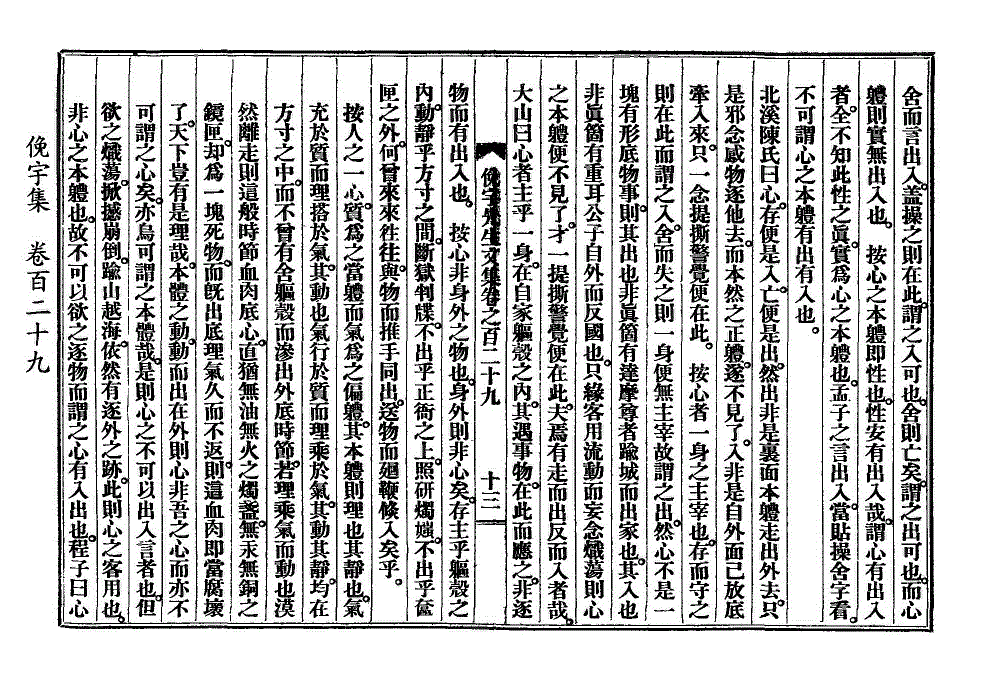 舍而言出入。盖操之则在此。谓之入可也。舍则亡矣。谓之出可也。而心体则实无出入也。 按心之本体即性也。性安有出入哉。谓心有出入者。全不知此性之真。实为心之本体也。孟子之言出入。当贴操舍字看。不可谓心之本体有出有入也。
舍而言出入。盖操之则在此。谓之入可也。舍则亡矣。谓之出可也。而心体则实无出入也。 按心之本体即性也。性安有出入哉。谓心有出入者。全不知此性之真。实为心之本体也。孟子之言出入。当贴操舍字看。不可谓心之本体有出有入也。北溪陈氏曰心。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里面本体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体。遂不见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牵入来。只一念提撕警觉便在此。 按心者一身之主宰也。存而守之则在此而谓之入。舍而失之则一身便无主宰故谓之出。然心不是一块有形底物事。则其出也非真个有达摩尊者踰城而出家也。其入也非真个有重耳公子自外而反国也。只缘客用流动而妄念炽荡则心之本体便不见了。才一提撕警觉便在此。夫焉有走而出反而入者哉。大山曰心者主乎一身。在自家躯壳之内。其遇事物。在此而应之。非逐物而有出入也。 按心非身外之物也。身外则非心矣。存主乎躯壳之内。动静乎方寸之间。断狱判牒。不出乎正衙之上。照研烛媸。不出乎奁匣之外。何曾来来往往。与物而推手同出。送物而回鞭倏入矣乎。
按人之一心。质为之当体而气为之偏体。其本体则理也其静也。气充于质而理搭于气。其动也气行于质而理乘于气。其动其静。均在方寸之中。而不曾有舍躯壳而渗出外底时节。若理乘气而动也漠然离走则这般时节血肉底心。直犹无油无火之烛盏。无汞无铜之镜匣。却为一块死物。而既出底理气久而不返。则这血肉即当腐坏了。天下岂有是理哉。本体之动。动而出在外则心非吾之心而亦不可谓之心矣。亦乌可谓之本体哉。是则心之不可以出入言者也。但欲之炽荡。掀撼崩倒。踰山越海。依然有逐外之迹。此则心之客用也。非心之本体也。故不可以欲之逐物而谓之心有入出也。程子曰心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5L 页
 本无出入。这本字更宜着眼。
本无出入。这本字更宜着眼。李子曰心则一人之心。天地之心。充满天地之间。安有出入之处。
问心有限量乎。程子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能通乎道。何限量之有。 按性者心之体也而无极之真也。天下之理。皆由此而出。安有理外底物事耶。惟其局于气而蔽于欲则达道不行。而咫尺之间。已非吾心境界。若通乎道。万物皆备于我。天下不足以大。何限量之有。既无限量则出入不足言也。
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 按人之一心。大本卓然而妙用流行者。斯谓之活。正犹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而不滞于一时一物也。心有所滞则胶柱也泥絮也死物也。是以人心常要活。活则周流而不滞于一隅。不滞于一隅则天地之间。皆莫非此心之境界也。自己境内。何须言出入乎。
张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按天心人心。只是一理。而天心之大。既无内外。则人之心。亦岂可有内外耶。其有内外者。局于气也。不局于气则上合天心。而天心本无出入。观天心则人心可见。
张子曰心大则百物皆通。 按理不局于气则心大。心不蔽于物则物通。心大则心不囿于物内。物通则物无在于心外。心既无内外则更安有出入哉。
上蔡谢氏曰心岂有出入远近精粗之间。 按远而四海之外。近而一身之间。粗而事物之著。精而义理之微。莫不管摄乎此心。则应接乎远者粗者而非出也。究验乎近者精者而非入也。既无间隔则自无出入。朱子曰心虽主乎一身。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论。 按心为一身之主宰。而心之理即天下之理也。物莫不有各具之理。而物之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6H 页
 即吾心之理也。既是一理则将以何者为内为精。而何者为外为粗也。管之者只在此。而不外者亦只在此。则虽欲言出入。不可得矣。
即吾心之理也。既是一理则将以何者为内为精。而何者为外为粗也。管之者只在此。而不外者亦只在此。则虽欲言出入。不可得矣。大山曰心虽主乎一身。而体与天地同。其大用与天地相流通。四海六合皆心之境界。故敛在方寸而非其入。应事接物而不可谓之出也。 按吾之心仁义礼智之体。即天之心元亨利贞之体也。吾之心爱恭宜别之用。即天之心生长收藏之用。此所谓同体同用而四海六合皆天心之境界。则其为吾心之境界亦可见矣。在方寸应事物。皆在境界之内。则境界内自不须言出入。
寒洲曰既谓虽在于一身之中而实有以管摄天下之理。则心之居所不移。酬酢万变。先生已备言之矣。何尝有东西驰骛。随处布列之意乎。古人言心。或曰升而天飞。降而渊沦。或曰一瞬之间。再抚四海。此果皆真谓此心泛无止舍。分布宇内耶。 按此为葛庵先生出入说。而略有所论者也。此所谓先生。盖指退陶也。心之无出入云者。以其不出乎方寸之间。管摄乎天下之理也。其所谓充满天地之间者。何尝谓其犹大雾之漫空洪水之滔天也哉。特以天下万物。无一非此心之用。故指言此心之无限量无内外。而不可以出入言耳。洲上此论。紧发明退陶之意。故取以著之。
按心者太极之全体也。朱子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者是也。吾心之理。即天地之一太极也。事物之理。即万物各具之太极也。各具之太极。本非在于一太极之外也。一太极。即各具太极之全体也。大而天地亦太极。细而事物亦太极。则何者非太极境界也。太极何自而有内外乎。心之动静。即太极之动静也。收敛于方寸之中。而方寸亦心之境界。应接天下之物。而天下亦心之境界也。故子思言性情之德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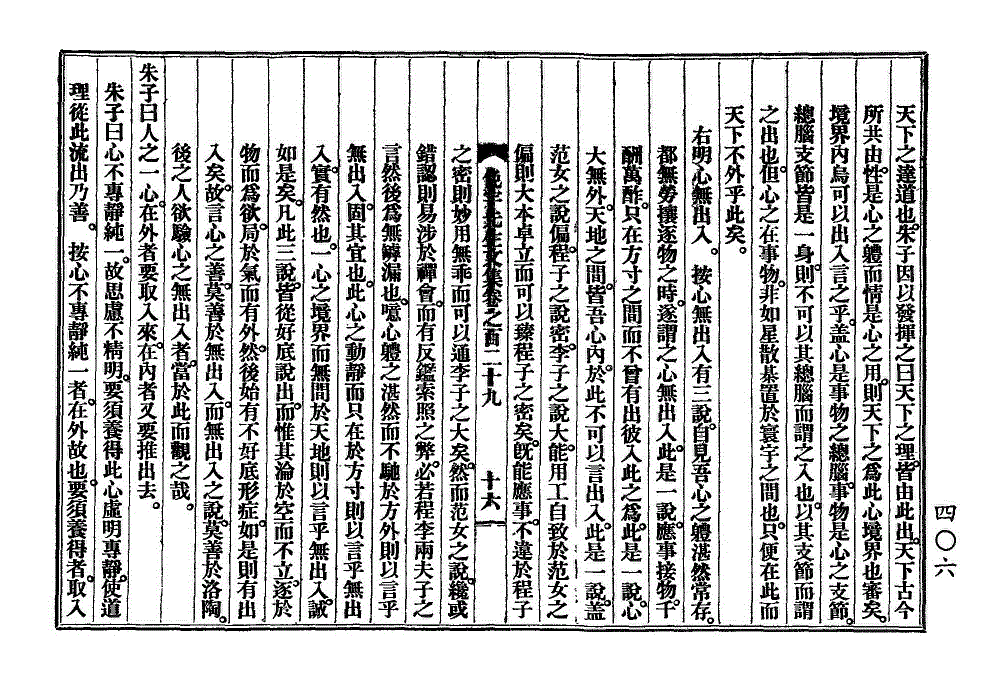 天下之达道也。朱子因以发挥之曰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天下古今所共由。性是心之体而情是心之用。则天下之为此心境界也审矣。境界内乌可以出入言之乎。盖心是事物之总脑。事物是心之支节。总脑支节皆是一身。则不可以其总脑而谓之入也。以其支节而谓之出也。但心之在事物。非如星散棋置于寰宇之间也。只便在此而天下不外乎此矣。
天下之达道也。朱子因以发挥之曰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天下古今所共由。性是心之体而情是心之用。则天下之为此心境界也审矣。境界内乌可以出入言之乎。盖心是事物之总脑。事物是心之支节。总脑支节皆是一身。则不可以其总脑而谓之入也。以其支节而谓之出也。但心之在事物。非如星散棋置于寰宇之间也。只便在此而天下不外乎此矣。右明心无出入。 按心无出入有三说。自见吾心之体湛然常存。都无劳攘逐物之时。遂谓之心无出入。此是一说。应事接物。千酬万酢。只在方寸之间而不曾有出彼入此之为。此是一说。心大无外。天地之间。皆吾心内。于此不可以言出入。此是一说。盖范女之说偏。程子之说密。李子之说大。能用工自致于范女之偏则大本卓立而可以臻程子之密矣。既能应事。不违于程子之密则妙用无乖而可以通李子之大矣。然而范女之说。才或错认则易涉于禅会。而有反鉴索照之弊。必若程李两夫子之言然后为无罅漏也。噫心体之湛然而不驰于方外则以言乎无出入。固其宜也。此心之动静而只在于方寸则以言乎无出入。实有然也。一心之境界而无间于天地则以言乎无出入。诚如是矣。凡此三说。皆从好底说出。而惟其沦于空而不立。逐于物而为欲。局于气而有外。然后始有不好底形症。如是则有出入矣。故言心之善。莫善于无出入。而无出入之说。莫善于洛陶。后之人欲验心之无出入者。当于此而观之哉。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取入来。在内者又要推出去。
朱子曰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要须养得此心虚明专静。使道理从此流出乃善。 按心不专静纯一者。在外故也。要须养得者。取入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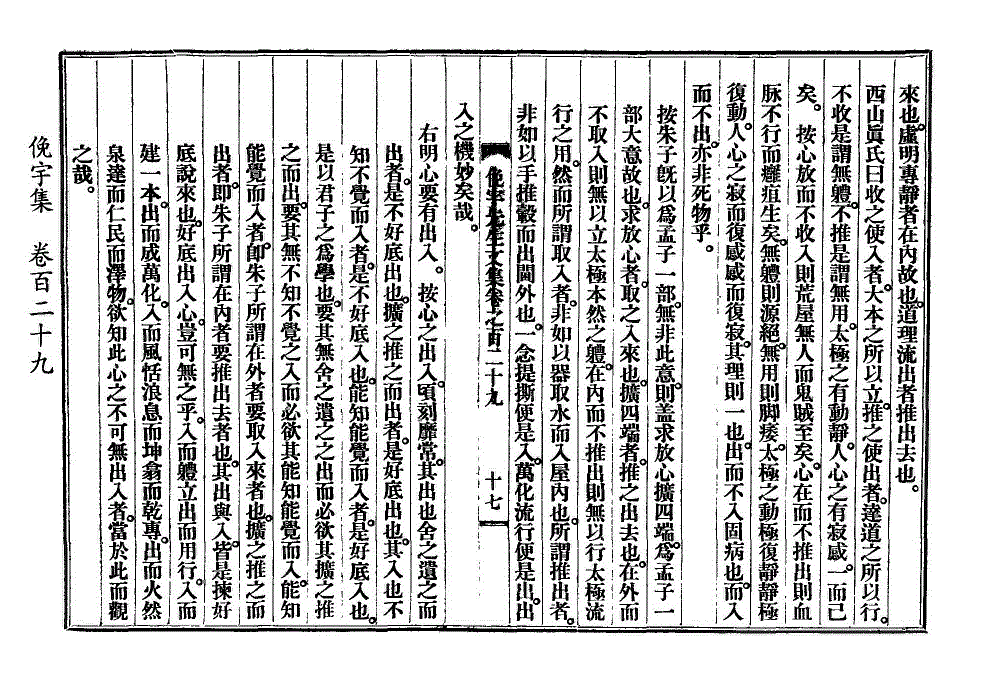 来也。虚明专静者在内故也。道理流出者推出去也。
来也。虚明专静者在内故也。道理流出者推出去也。西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达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谓无体。不推是谓无用。太极之有动静。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按心放而不收入则荒屋无人而鬼贼至矣。心在而不推出则血脉不行而痈疽生矣。无体则源绝。无用则脚痿。太极之动极复静静极复动。人心之寂而复感感而复寂。其理则一也。出而不入固病也。而入而不出。亦非死物乎。
按朱子既以为孟子一部。无非此意。则盖求放心扩四端。为孟子一部大意故也。求放心者。取之入来也。扩四端者。推之出去也。在外而不取入则无以立太极本然之体。在内而不推出则无以行太极流行之用。然而所谓取入者。非如以器取水而入屋内也。所谓推出者。非如以手推毂而出阃外也。一念提撕便是入。万化流行便是出。出入之机妙矣哉。
右明心要有出入。 按心之出入。顷刻靡常。其出也舍之遗之而出者。是不好底出也。扩之推之而出者。是好底出也。其入也不知不觉而入者。是不好底入也。能知能觉而入者。是好底入也。是以君子之为学也。要其无舍之遗之之出而必欲其扩之推之而出。要其无不知不觉之入而必欲其能知能觉而入。能知能觉而入者。即朱子所谓在外者要取入来者也。扩之推之而出者。即朱子所谓在内者要推出去者也。其出与入。皆是拣好底说来也。好底出入心。岂可无之乎。入而体立出而用行。入而建一本。出而成万化。入而风恬浪息而坤翕而乾专。出而火然泉达而仁民而泽物。欲知此心之不可无出入者。当于此而观之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7L 页
 礼记曰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礼记曰非僻之心。无自入也。方氏曰心内也而言入何哉。盖心虽在内。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则与物俱入。故以入言焉。 按方氏此说。似涉于闪铄恍惚之病。而究其出入之由。则其实相不外乎此。此心寂然而外物触之而动。则是物探心而出也。外物纷然而此心引之而来。则是心与物而入也。其出其入。皆在瞥乍之间。不待及其久也。然后心与物入也。及其久也四字。当在商量。
西山真氏曰惰慢之气。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气。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设于身体。则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体。内而心知。皆由顺正以行其义。 按惰慢之气。气昏而理不摄者也。邪僻之气。物触而气相感者也。惰慢气邪僻气。俱是心气。而初非别气也。但惰慢之气。由身而作故曰出。邪僻之气。因物而生故曰入。既谓之气则其非心之本体则明矣。但乖气之胜。本体之正遂不见了。使二者之气不得设于身体者。敬义夹持之之工也。此所以心知之正而百体之莫不从令也。
按非僻之心。非别有一个心从外而入也。物之非僻。才感于此心。而心之客用。拖带得这物来。其出也为妄动而炽荡之情作焉。其入也为留滞而胶扰之病在焉。是以古之君子。车必听銮和。行必鸣佩玉。醒起了此心而无妄动之患。清息了此心而无留滞之症。此所以邪念之无自出而僻气之无自入也与。
右明心要无出入。 按此个出入。即所谓舍之遗之而出也。不知不觉而入也。其出其入。皆指那不好底言之也。出而用乖。入而体偏。出而千邪万恶。入而三头两绪。出而荒溪曲径而遗却明程。入而云滃雾滚而滓秽太清。欲知心之不可有出入者。当于此而观之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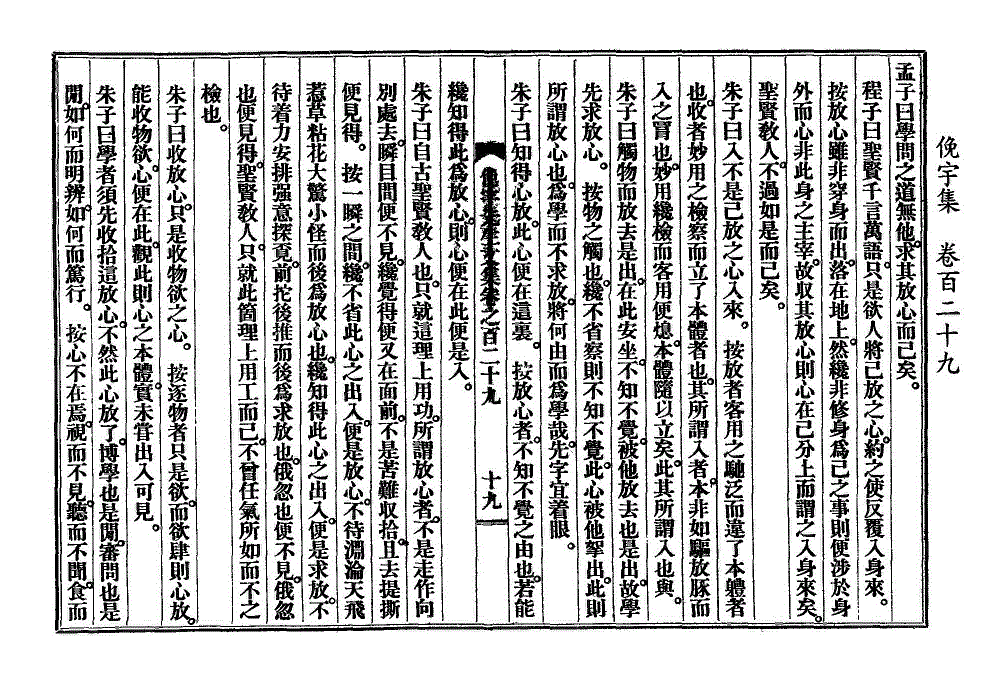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覆入身来。 按放心虽非穿身而出。落在地上。然才非修身为己之事则便涉于身外而心非此身之主宰。故收其放心则心在己分上而谓之入身来矣。圣贤教人。不过如是而已矣。
朱子曰入不是已放之心入来。 按放者客用之驰泛而违了本体者也。收者妙用之检察而立了本体者也。其所谓入者。本非如驱放豚而入之罥也。妙用才检而客用便熄。本体随以立矣。此其所谓入也与。
朱子曰触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觉。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学先求放心。 按物之触也。才不省察则不知不觉。此心被他挐出。此则所谓放心也。为学而不求放。将何由而为学哉。先字宜着眼。
朱子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这里。 按放心者。不知不觉之由也。若能才知得此为放心。则心便在此便是入。
朱子曰自古圣贤教人也。只就这理上用功。所谓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别处去。瞬目间便不见。才觉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难收拾。且去提撕便见得。 按一瞬之间。才不省此心之出入。便是放心。不待渊沦天飞惹草粘花大惊小怪而后为放心也。才知得此心之出入。便是求放。不待着力安排强意探觅。前拖后推而后为求放也。俄忽也便不见。俄忽也便见得。圣贤教人。只就此个理上用工而已。不曾任气所如而不之检也。
朱子曰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 按逐物者只是欲。而欲肆则心放。能收物欲。心便在此。观此则心之本体。实未尝出入可见。
朱子曰学者须先收拾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学也是閒。审问也是閒。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笃行。 按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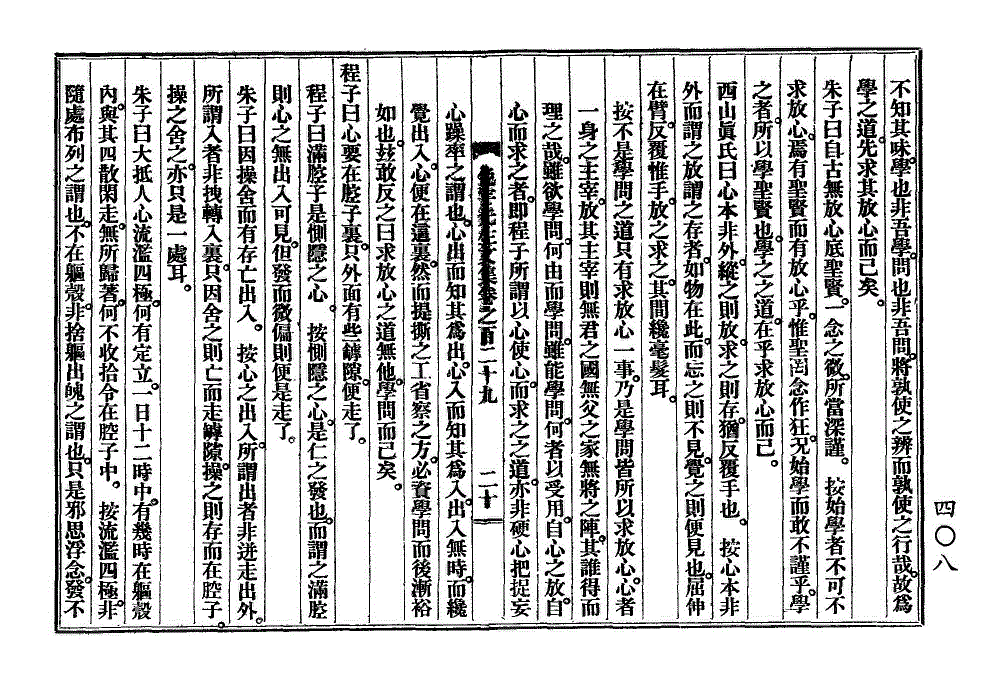 不知其味。学也非吾学。问也非吾问。将孰使之辨而孰使之行哉。故为学之道。先求其放心而已矣。
不知其味。学也非吾学。问也非吾问。将孰使之辨而孰使之行哉。故为学之道。先求其放心而已矣。朱子曰自古无放心底圣贤。一念之微。所当深谨。 按始学者不可不求放心。焉有圣贤而有放心乎。惟圣罔念作狂。况始学而敢不谨乎。学之者。所以学圣贤也。学之之道。在乎求放心而已。
西山真氏曰心本非外。纵之则放。求之则存。犹反覆手也。 按心本非外而谓之放谓之存者。如物在此。而忘之则不见。觉之则便见也。屈伸在臂。反覆惟手。放之求之。其间才毫发耳。
按不是学问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学问皆所以求放心。心者一身之主宰。放其主宰则无君之国无父之家无将之阵。其谁得而理之哉。虽欲学问。何由而学问。虽能学问。何者以受用。自心之放。自心而求之者。即程子所谓以心使心。而求之之道。亦非硬心把捉妄心躁率之谓也。心出而知其为出。心入而知其为入。出入无时。而才觉出入。心便在这里。然而提撕之工省察之方。必资学问而后渐裕如也。玆敢反之曰求放心之道无他。学问而已矣。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里。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程子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 按恻隐之心。是仁之发也。而谓之满腔则心之无出入可见。但发而微偏则便是走了。
朱子曰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 按心之出入。所谓出者非迸走出外。所谓入者非拽转入里。只因舍之则亡而走罅隙。操之则存而在腔子。操之舍之。亦只是一处耳。
朱子曰大抵人心流滥四极。何有定立。一日十二时中。有几时在躯壳内。与其四散闲走。无所归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 按流滥四极。非随处布列之谓也。不在躯壳。非舍躯出魄之谓也。只是邪思浮念。发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9H 页
 在己分上者。便是流滥四极。便是不在躯壳。在躯壳则可以管摄乎四极。而滥四极则无由主宰乎躯壳。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
在己分上者。便是流滥四极。便是不在躯壳。在躯壳则可以管摄乎四极。而滥四极则无由主宰乎躯壳。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朱子曰程子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耶。 按应事接物。务要存心。若应事而心都奔在这事上。接物而心都奔在这物上。则此心几非在我。而将身之不知何由而应事物哉。此程子所以心要在腔子里。
朱子曰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 按心不在身。故无以检身。能察则心便在。而敬以直则无罅隙。
问如何在腔子里。朱子曰敬便在腔子里。 按心为一身之主宰。而敬为一心之主宰。不敬则心无主宰而身无主宰矣。能敬则心有主宰而身有主宰矣。隙与不隙。专在乎敬与不敬。为心学者可不敬哉。
按腔字从肉从空。统而言则肉体之空处也。密而言则肉心之空处也。当体之心。在乎肉体之空。而本体之心。搭乎肉心之空处。其本相如是。则心不待要在而在里。然心之神明。动静无时。动而横奔则如不垣之屋。路通四街。静而偏陷则如无底之瓶。水渗当处。然而其所谓罅隙者。非谓血肉之上𦉝下齾也。躯壳之窍。皆穴胸也。外物之来。才不检防则便是有罅隙。由其不检而役于外物。便是走了。程夫子示人切要之意。已极无馀。而朱夫子又以一敬字拈示其单方。先师所以嘉惠后学者至矣。呜乎韪哉。
程子曰心岂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操之之道。敬以直内而已。
有言未感时。知何所寓。程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更怎生寻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 按未感物时。疑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09L 页
 若在这里然。细究而推之则虽在未感。亦有出入。今有宅长。虽在家内。不顾家务。无所整理。则是亦出而已矣。随事综画。主张家务。则是为入也已。心之未感。其出入存亡亦如是也。怎生寻所寓。欲知所寓。只有操之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而已。
若在这里然。细究而推之则虽在未感。亦有出入。今有宅长。虽在家内。不顾家务。无所整理。则是亦出而已矣。随事综画。主张家务。则是为入也已。心之未感。其出入存亡亦如是也。怎生寻所寓。欲知所寓。只有操之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而已。程子曰以敬直内则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则直矣。 按敬以直内则会动会静。一循天则。无急促苟且之病。以敬直内则着力扶持。用心躁扰。无宽閒平远之意。存之不弛。处之不迫。则敬立而内自直矣。
上蔡谢氏曰事至应之。不与之往。非敬乎。万物之变而此常存。奚纷扰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谓此耳。 按敬不立则内不直。内不直则屈于外而逐于物矣。心有主宰则物来而心不往。物变而心常存。何尝有纷扰之患。此所以事思敬云。
和靖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则百事不敢轻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习之既久。自然有所得矣。 按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则百事不敢轻为。不敢妄作矣。未出门使民时。俨若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则不愧屋漏矣。但觉见有些子放去。便收敛提掇起。常常相接。则久后自熟。熟则自久。久则有得。得则无所失。
朱子曰人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 按心出心入。专在于操之舍之。则出入上有何工夫。只去操舍上用工。有操而无舍则此心之体。无亡而有存。无出而有入。
朱子曰孟子求放心语已是宽。若居处恭执事敬二语。更无馀欠。 按孟子言求放心而不言求之之方。故谓之宽。若夫子所谓居处恭执事敬二句则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动静不违。表里交正。则奚放心之有。此所以无馀欠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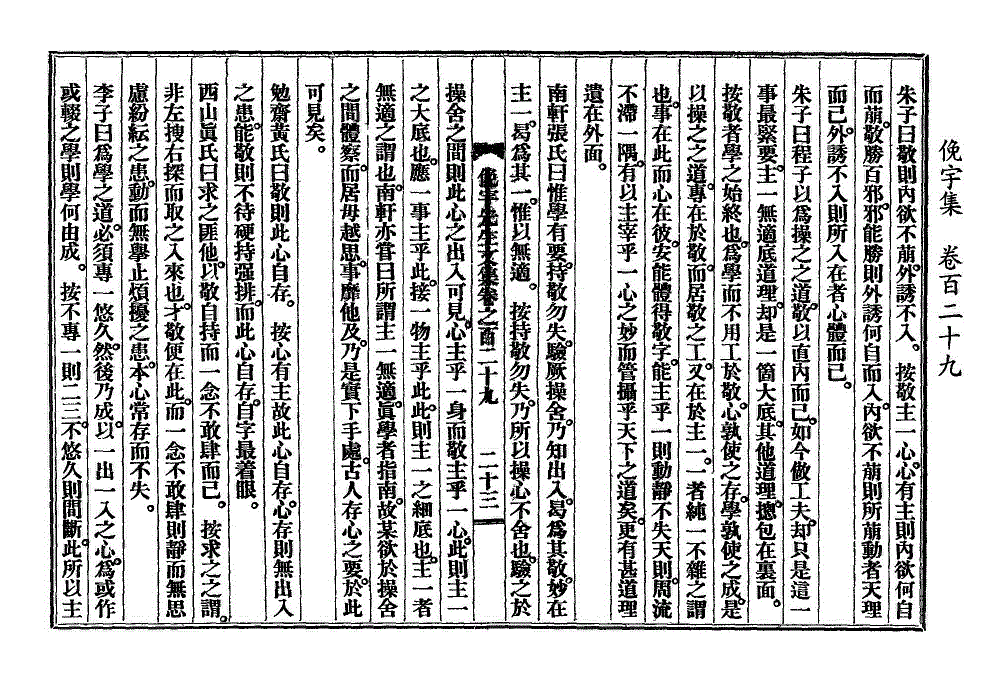 朱子曰敬则内欲不萌。外诱不入。 按敬主一心。心有主则内欲何自而萌。敬胜百邪。邪能胜则外诱何自而入。内欲不萌则所萌动者天理而已。外诱不入则所入在者心体而已。
朱子曰敬则内欲不萌。外诱不入。 按敬主一心。心有主则内欲何自而萌。敬胜百邪。邪能胜则外诱何自而入。内欲不萌则所萌动者天理而已。外诱不入则所入在者心体而已。朱子曰程子以为操之之道。敬以直内而已。如今做工夫。却只是这一事最紧要。主一无适底道理。却是一个大底。其他道理。总包在里面。 按敬者学之始终也。为学而不用工于敬。心孰使之存。学孰使之成。是以操之之道。专在于敬。而居敬之工。又在于主一。一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能主乎一则动静不失天则。周流不滞一隅。有以主宰乎一心之妙而管摄乎天下之道矣。更有甚道理遗在外面。
南轩张氏曰惟学有要。持敬勿失。验厥操舍。乃知出入。曷为其敬。妙在主一。曷为其一。惟以无适。 按持敬勿失。乃所以操心不舍也。验之于操舍之间则此心之出入可见。心主乎一身而敬主乎一心。此则主一之大底也。应一事主乎此。接一物主乎此。此则主一之细底也。主一者无适之谓也。南轩亦尝曰所谓主一无适。真学者指南。故某欲于操舍之间体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实下手处。古人存心之要。于此可见矣。
勉斋黄氏曰敬则此心自存。 按心有主故此心自存。心存则无出入之患。能敬则不待硬持强排。而此心自存。自字最着眼。
西山真氏曰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 按求之之谓。非左搜右探而取之入来也。才敬便在此。而一念不敢肆则静而无思虑纷纭之患。动而无举止烦扰之患。本心常存而不失。
李子曰为学之道。必须专一悠久。然后乃成。以一出一入之心。为或作或辍之学则学何由成。 按不专一则二三。不悠久则间断。此所以主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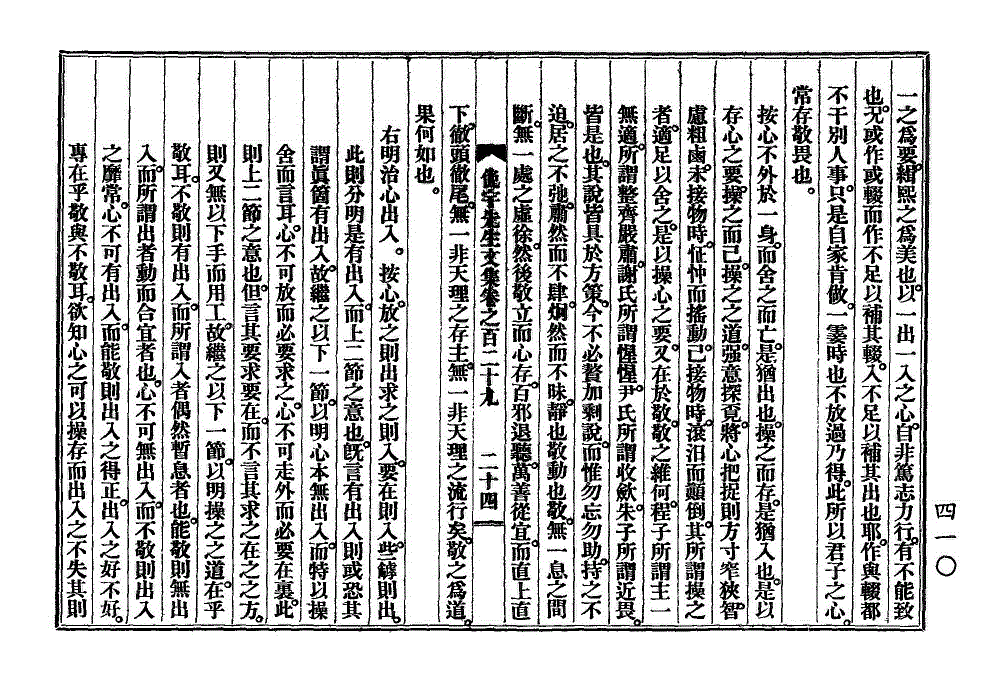 一之为要。缉熙之为美也。以一出一入之心。自非笃志力行。有不能致也。况或作或辍而作不足以补其辍。入不足以补其出也耶。作与辍都不干别人事。只是自家肯做。一霎时也不放过乃得。此所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也。
一之为要。缉熙之为美也。以一出一入之心。自非笃志力行。有不能致也。况或作或辍而作不足以补其辍。入不足以补其出也耶。作与辍都不干别人事。只是自家肯做。一霎时也不放过乃得。此所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也。按心不外于一身。而舍之而亡。是犹出也。操之而存。是犹入也。是以存心之要。操之而已。操之之道。强意探觅。将心把捉则方寸窄狭。智虑粗卤。未接物时。怔忡而摇动。已接物时。滚汩而颠倒。其所谓操之者。适足以舍之。是以操心之要。又在于敬。敬之维何。程子所谓主一无适。所谓整齐严肃。谢氏所谓惺惺。尹氏所谓收敛。朱子所谓近畏。皆是也。其说皆具于方策。今不必赘加剩说。而惟勿忘勿助。持之不迫。居之不弛。肃然而不肆。炯然而不昧。静也敬动也敬。无一息之间断。无一处之虚徐。然后敬立而心存。百邪退听。万善从宜。而直上直下。彻头彻尾。无一非天理之存主。无一非天理之流行矣。敬之为道。果何如也。
右明治心出入。 按心。放之则出求之则入。要在则入。些罅则出。此则分明是有出入。而上二节之意也。既言有出入则或恐其谓真个有出入。故继之以下一节。以明心本无出入。而特以操舍而言耳。心不可放而必要求之。心不可走外而必要在里。此则上二节之意也。但言其要求要在。而不言其求之在之之方。则又无以下手而用工。故继之以下一节。以明操之之道。在乎敬耳。不敬则有出入。而所谓入者偶然暂息者也。能敬则无出入。而所谓出者动而合宜者也。心不可无出入。而不敬则出入之靡常。心不可有出入。而能敬则出入之得正。出入之好不好。专在乎敬与不敬耳。欲知心之可以操存而出入之不失其则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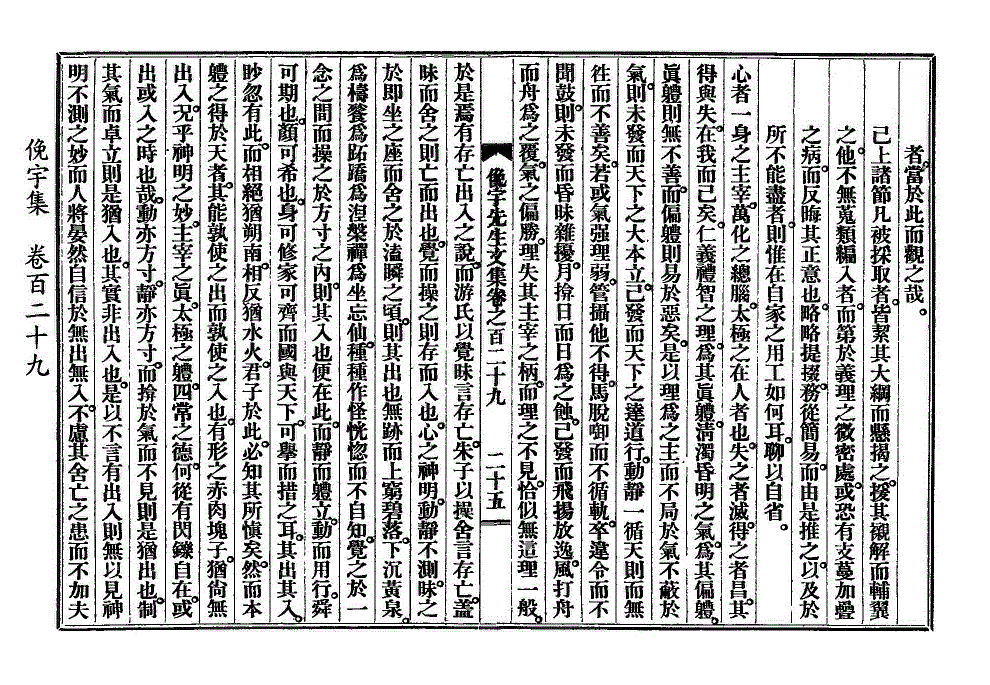 者。当于此而观之哉。
者。当于此而观之哉。已上诸节凡被采取者。皆絜其大纲而悬揭之。援其衬解而辅翼之。他不无蒐类编入者。而第于义理之微密处。或恐有支蔓加叠之病。而反晦其正意也。略略提掇。务从简易。而由是推之。以及于所不能尽者。则惟在自家之用工如何耳。聊以自省。
心者一身之主宰。万化之总脑。太极之在人者也。失之者灭。得之者昌。其得与失。在我而已矣。仁义礼智之理。为其真体。清浊昏明之气。为其偏体。真体则无不善。而偏体则易于恶矣。是以理为之主而不局于气不蔽于气。则未发而天下之大本立。已发而天下之达道行。动静一循天则而无往而不善矣。若或气强理弱。管摄他不得。马脱衔而不循轨。卒违令而不闻鼓。则未发而昏昧杂扰。月掩日而日为之蚀。已发而飞扬放逸。风打舟而舟为之覆。气之偏胜。理失其主宰之柄。而理之不见。恰似无这理一般。于是焉有存亡出入之说。而游氏以觉昧言存亡。朱子以操舍言存亡。盖昧而舍之则亡而出也。觉而操之则存而入也。心之神明。动静不测。昧之于即坐之座而舍之于溘瞬之顷。则其出也无迹而上穷碧落。下沉黄泉。为梼餮为蹠蹻为涅槃禅为坐忘仙。种种作怪恍惚而不自知。觉之于一念之间而操之于方寸之内。则其入也便在此。而静而体立。动而用行。舜可期也。颜可希也。身可修家可齐而国与天下。可举而措之耳。其出其入。眇忽有此。而相绝犹朔南。相反犹水火。君子于此。必知其所慎矣。然而本体之得于天者。其能孰使之出而孰使之入也。有形之赤肉块子。犹尚无出入。况乎神明之妙。主宰之真。太极之体。四常之德。何从有闪铄自在。或出或入之时也哉。动亦方寸。静亦方寸。而掩于气而不见则是犹出也。制其气而卓立则是犹入也。其实非出入也。是以不言有出入则无以见神明不测之妙而人将晏然自信于无出无入。不虑其舍亡之患而不加夫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1L 页
 操存之功矣。不言无出入则无以见本体自在之真。而人将求之于窈冥踔绝之域。而流眸望气。伸手撮空。思有以攫将取挐将来。而不知提撕警觉于躯壳之内矣。于是收而入之。推而出之。未接物时。大本卓立。知觉专静而怠惰之心无由内出。既应物时。妙用流行。品节不差。而非僻之心。无由外入。推之于是则出入之臧否。可得以验矣。然而人心之机。易动而难静。常人之心。多动而少静。出入之失。恒在于是。静而扶之竖之守之成之。动而省之察之节之制之。非敬不能也。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矣。苟欲存心。舍敬奚以哉。不主乎敬而存心。将未免把一个心。去捉一个心。而愈捉而愈不存。里面已三头两绪。奚暇于应外乎。前圣后圣相继发明。而一心之形症。治心之节度。已纤悉而无馀矣。以言其操纵之机则如海舶之有柁。以言其动静之机则如风灶之有棙。以言其分合之妙则玉钥开喉。以言其存主之要则彩笔点睛。真诠秘函。次第禅承。而生乎后世者。不过因是以推之耳。奈何微言日堙。偏见朋起。守其有出入者则将心为风影。守其无出入者则认心为土墣。纷纶于颊舌之间而不曾究之于圣人之言。取之于自家之身。适足以乱吾真而已。果何补哉。钟锡学不通方。智不烛幽。而其于此说之互相异同。窃尝不无疑于心矣。于是历考往训。反覆参覈。而亦尝反求而躬验之。积力之久。若有见焉。乃敢摭采群书。分类立门。僭附瞽说。證其异同。合为一说。以便观省。其于圣人之心法。虽未必真造的契。而亦可以此而订稗说之偏云耳。壬申暮春谨述。
操存之功矣。不言无出入则无以见本体自在之真。而人将求之于窈冥踔绝之域。而流眸望气。伸手撮空。思有以攫将取挐将来。而不知提撕警觉于躯壳之内矣。于是收而入之。推而出之。未接物时。大本卓立。知觉专静而怠惰之心无由内出。既应物时。妙用流行。品节不差。而非僻之心。无由外入。推之于是则出入之臧否。可得以验矣。然而人心之机。易动而难静。常人之心。多动而少静。出入之失。恒在于是。静而扶之竖之守之成之。动而省之察之节之制之。非敬不能也。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矣。苟欲存心。舍敬奚以哉。不主乎敬而存心。将未免把一个心。去捉一个心。而愈捉而愈不存。里面已三头两绪。奚暇于应外乎。前圣后圣相继发明。而一心之形症。治心之节度。已纤悉而无馀矣。以言其操纵之机则如海舶之有柁。以言其动静之机则如风灶之有棙。以言其分合之妙则玉钥开喉。以言其存主之要则彩笔点睛。真诠秘函。次第禅承。而生乎后世者。不过因是以推之耳。奈何微言日堙。偏见朋起。守其有出入者则将心为风影。守其无出入者则认心为土墣。纷纶于颊舌之间而不曾究之于圣人之言。取之于自家之身。适足以乱吾真而已。果何补哉。钟锡学不通方。智不烛幽。而其于此说之互相异同。窃尝不无疑于心矣。于是历考往训。反覆参覈。而亦尝反求而躬验之。积力之久。若有见焉。乃敢摭采群书。分类立门。僭附瞽说。證其异同。合为一说。以便观省。其于圣人之心法。虽未必真造的契。而亦可以此而订稗说之偏云耳。壬申暮春谨述。理诀上(丁丑)
理为气先
一古之初。阴阳未生。而已有太极。太极才动。便生一阳。动极才静。便生一阴。理之生气。间不容发。然不先有动底理。阳何自生。不先有静底理。阴何自生。理也者。阴阳之父。天地万物之祖。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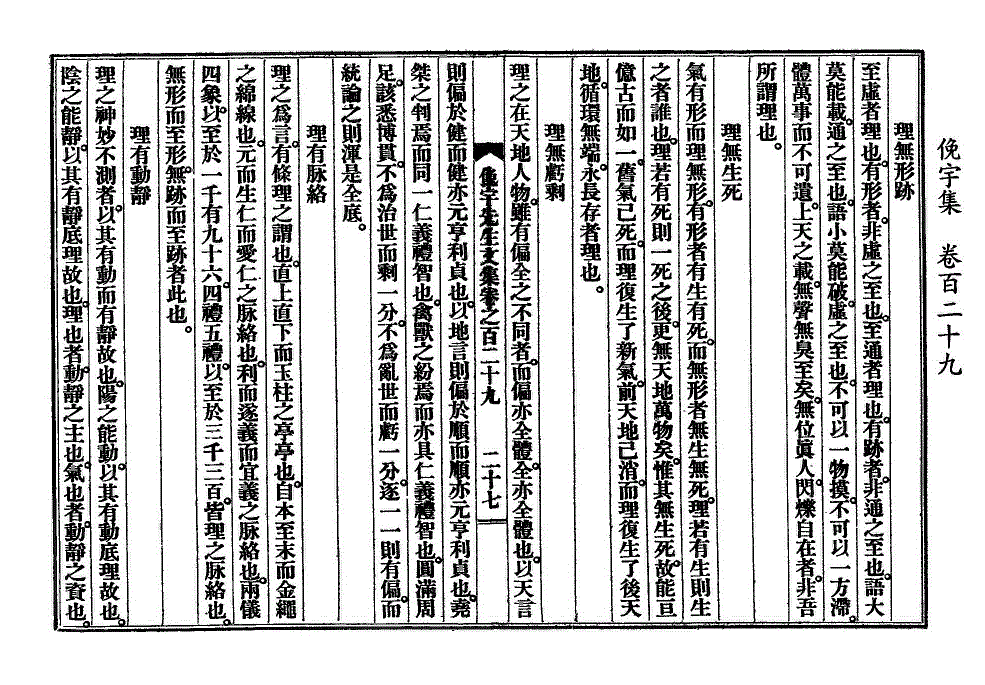 理无形迹
理无形迹至虚者理也。有形者。非虚之至也。至通者理也。有迹者。非通之至也。语大莫能载。通之至也。语小莫能破。虚之至也。不可以一物摸。不可以一方滞。体万事而不可遗。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无位真人。闪烁自在者。非吾所谓理也。
理无生死
气有形而理无形。有形者有生有死。而无形者无生无死。理若有生则生之者谁也。理若有死则一死之后。更无天地万物矣。惟其无生死。故能亘亿古而如一。旧气已死。而理复生了新气。前天地已消。而理复生了后天地。循环无端。永长存者理也。
理无亏剩
理之在天地人物。虽有偏全之不同者。而偏亦全体。全亦全体也。以天言则偏于健而健亦元亨利贞也。以地言则偏于顺而顺亦元亨利贞也。尧桀之判焉而同一仁义礼智也。禽兽之纷焉而亦具仁义礼智也。圆满周足。该悉博贯。不为治世而剩一分。不为乱世而亏一分。逐一一则有偏。而统论之则浑是全底。
理有脉络
理之为言。有条理之谓也。直上直下而玉柱之亭亭也。自本至末而金绳之绵线也。元而生仁而爱仁之脉络也。利而遂义而宜义之脉络也。两仪四象。以至于一千有九十六。四礼五礼。以至于三千三百。皆理之脉络也。无形而至形。无迹而至迹者此也。
理有动静
理之神妙不测者。以其有动而有静故也。阳之能动。以其有动底理故也。阴之能静。以其有静底理故也。理也者。动静之主也。气也者。动静之资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2L 页
 理之冲漠。无间于动静。气之屈伸。易见于形迹。故气马背上。理为泥塑久矣。非至明。孰能见之。
理之冲漠。无间于动静。气之屈伸。易见于形迹。故气马背上。理为泥塑久矣。非至明。孰能见之。理有体用
冲漠无眹者体也。随遇发见者用也。寂然不动者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用也。万象森然而体中有用。品节不差而用中有体。理体气用则理无用而气无体矣。理不能随遇发见。而又不能通天下之故。则所贵乎理者甚么。
理为主宰
在天曰帝。在人曰心。主乎静而宰乎动。四德圆而万化顺。五性正而百行修。气之腾倒。理失其主宰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遂以贞藏。以仁爱以礼恭以义宜以智别。而其以之者主宰也。理之一者也。元亨利贞。仁义礼智。理之殊者也。以一理而妙众理。主宰之谓也。
理无有不善
至虚故无累。至灵故妙万物而不差。至实故体万物而皆真。木有曲直而其理则仁也。金有精粗而其理则义也。桀蹠之恶焉而见孺子之入井则莫不有恻隐之心。路人之愚焉而语未发之本真则与尧舜一样矣。其有不善者。气之罪也。
恶亦不可不谓之理
凡有恶者。固气之为祟。然气而无理。亦做出恶不得。是以其为恶也。为之者固气也。而为者即理也。然而理之本体。何尝有恶哉。惟其动而气汩之掩之逆之荡之。如人君之受制于强臣。而蒙其昏险之名。恶亦不可不谓之理者。责备于贤者也。
理诀中
性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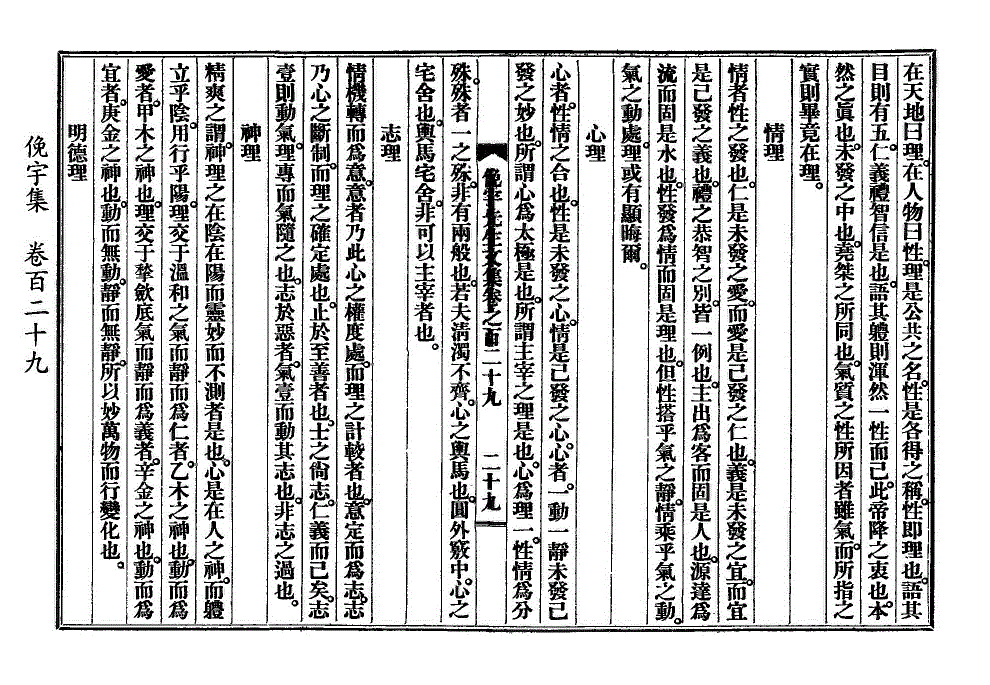 在天地曰理。在人物曰性。理是公共之名。性是各得之称。性即理也。语其目则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语其体则浑然一性而已。此帝降之衷也。本然之真也。未发之中也。尧桀之所同也。气质之性所因者虽气。而所指之实则毕竟在理。
在天地曰理。在人物曰性。理是公共之名。性是各得之称。性即理也。语其目则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语其体则浑然一性而已。此帝降之衷也。本然之真也。未发之中也。尧桀之所同也。气质之性所因者虽气。而所指之实则毕竟在理。情理
情者性之发也。仁是未发之爱。而爱是已发之仁也。义是未发之宜。而宜是已发之义也。礼之恭智之别。皆一例也。主出为客而固是人也。源达为流而固是水也。性发为情而固是理也。但性搭乎气之静。情乘乎气之动。气之动处。理或有显晦尔。
心理
心者。性情之合也。性是未发之心。情是已发之心。心者。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妙也。所谓心为太极是也。所谓主宰之理是也。心为理一。性情为分殊。殊者一之殊。非有两般也。若夫清浊不齐。心之舆马也。圆外窍中。心之宅舍也。舆马宅舍。非可以主宰者也。
志理
情机转而为意。意者乃此心之权度处。而理之计较者也。意定而为志。志乃心之断制。而理之确定处也。止于至善者也。士之尚志。仁义而已矣。志壹则动气。理专而气随之也。志于恶者。气壹而动其志也。非志之过也。
神理
精爽之谓。神理之在阴在阳而灵妙而不测者是也。心是在人之神。而体立乎阴。用行乎阳。理交于温和之气而静而为仁者。乙木之神也。动而为爱者。甲木之神也。理交于揫敛底气而静而为义者。辛金之神也。动而为宜者。庚金之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所以妙万物而行变化也。
明德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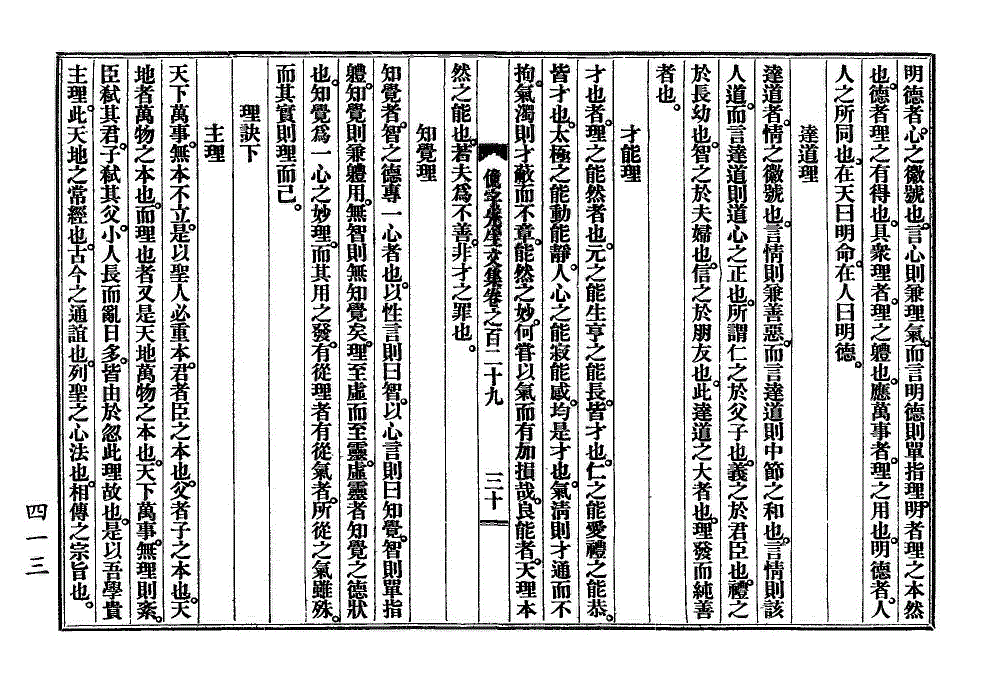 明德者。心之徽号也。言心则兼理气。而言明德则单指理。明者理之本然也。德者理之有得也。具众理者。理之体也。应万事者。理之用也。明德者。人人之所同也。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
明德者。心之徽号也。言心则兼理气。而言明德则单指理。明者理之本然也。德者理之有得也。具众理者。理之体也。应万事者。理之用也。明德者。人人之所同也。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达道理
达道者。情之徽号也。言情则兼善恶。而言达道则中节之和也。言情则该人道。而言达道则道心之正也。所谓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长幼也。智之于夫妇也。信之于朋友也。此达道之大者也。理发而纯善者也。
才能理
才也者。理之能然者也。元之能生亨之能长。皆才也。仁之能爱礼之能恭。皆才也。太极之能动能静。人心之能寂能感。均是才也。气清则才通而不拘。气浊则才蔽而不章。能然之妙。何尝以气而有加损哉。良能者。天理本然之能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知觉理
知觉者。智之德专一心者也。以性言则曰智。以心言则曰知觉。智则单指体。知觉则兼体用。无智则无知觉矣。理至虚而至灵。虚灵者知觉之德状也。知觉为一心之妙理。而其用之发。有从理者有从气者。所从之气虽殊。而其实则理而已。
理诀下
主理
天下万事。无本不立。是以圣人必重本。君者臣之本也。父者子之本也。天地者万物之本也。而理也者又是天地万物之本也。天下万事。无理则紊。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小人长而乱日多。皆由于忽此理故也。是以吾学贵主理。此天地之常经也。古今之通谊也。列圣之心法也。相传之宗旨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4H 页
 明理
明理学必先于明理。理不明则行不能不差矣。是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所以明此理也。格物致知之谓也。人心有知。事物有理。一理相感。本无彼此。知之真则理便在是矣。因其已知而益穷之。则气禀之拘。渐当发开。而物累之蔽。自当消融。天理莹然。触事瞭然。烛照龟卜。不足言矣。
循理
所贵乎主理而明理者。以其将顺之于行也。居敬所以存此理也。力行所以行此理也。复礼所以复此理也。父慈子孝君义臣忠诚意正心。以至于治国平天下。洒扫应对。以至于位天地育万物。动静一循天则而无过无不及者。皆所以循此理也。此圣人之极功。理学之实境也。可不勉哉。
理诀续上
理生气
太极动静而阴阳生焉。犹人之举止而肃然有风声也。元之理生温和之气。而甲之气生于动。乙之气生于静。亨之理生光明之气。而丙之气生于动。丁之气生于静。利之于庚辛。贞之于壬癸。皆其类也。诚为四德之实理。而戊己之冲气生焉。根于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而无穷。而气之始生。亦未尝不善。正犹赤子之初生。纯一无伪焉尔。
理资气
理气之相合。犹夫妇之相配。静而理搭乎气。相须以为体。动而理乘乎气。相待以为用。主宰者理也而资助者气也。体物者理也而运用者气也。发者理也而发之者气也。成者理也而成之者气也。气而无理则固不能妙万物而行化。而理而无气则亦不能有品汇而成功矣。固不可相杂。而亦不可相离者然也。
理养气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4L 页
 气者所以配夫理而行其化者。故气不可荡而暴之。亦不可梏而绝之。是以必集义以养之。主静以养之。主静而湛一之气生焉。集义而浩然之气长焉。湛一则滓脚融化而天理呈露矣。浩然则大勇刚直而天理霶沛矣。气非自养。理以养之也。父之养子。君之养民。理当然也。
气者所以配夫理而行其化者。故气不可荡而暴之。亦不可梏而绝之。是以必集义以养之。主静以养之。主静而湛一之气生焉。集义而浩然之气长焉。湛一则滓脚融化而天理呈露矣。浩然则大勇刚直而天理霶沛矣。气非自养。理以养之也。父之养子。君之养民。理当然也。理制气
气之不齐。升降飞扬上下往来清浊昏明竖倒无定。是以怪物兴小人长乱世至矣。气不可任之。必主理以制之。主敬以制邪慢之气。存诚以制夸伪之气。居仁以制残酷之气。由义以制柔懦之气。致知以制昏翳之气。约其情使不至于炽荡。持其志使不至于流逸。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听命焉。皆所以尊德性而黜客气。使乱臣贼子。不得作于世也。
理诀续下
理具理
太极浑然而万理森然。尺之有寸。衡之有星。自然之理也。吾心之明德。浑然一圈。而大分之则四性粲然。细分之则众理毕具。以一理而具众理。理之常也。理一之中。分未尝不殊。无寸之尺。无星之衡。物之贱者也。以此具此。夫焉有道器之别哉。
理妙理
天道继善而成性。人心检性而约情。皆理之妙理也。知为智之德而专一心而妙性情。敬为礼之德而专一心而妙动静。妙之者浑然而一者也。所妙者粲然而殊者也。以一理而宰众理。理之所以妙也。目不能视目。舌不能舐舌。有形者之局也。理之妙理。无形者之不测也。
中庸大支辨(丙子)
顷年癸酉春。余在峄山。南黎许先生专书劝图中庸支节以示之。余方苦愁恼无聊。且乏简编之可寓趣者。乐其因此拨遣。而有以资讲辨之益。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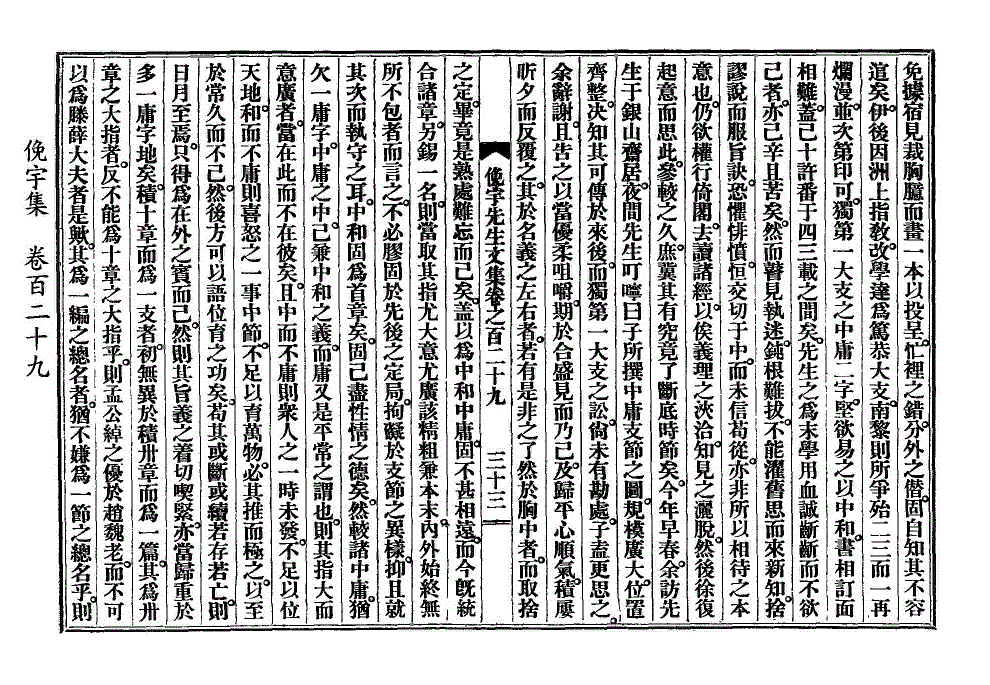 免据宿见裁胸臆而画一本以投呈。忙里之错。分外之僭。固自知其不容逭矣。伊后因洲上指教。改学达为笃恭大支。南黎则所争殆二三而一再烂漫。并次第印可。独第一大支之中庸二字。坚欲易之以中和。书相订面相难。盖已十许番于四三载之间矣。先生之为末学用血诚龂龂而不欲已者。亦已辛且苦矣。然而瞽见执迷。钝根难拔。不能濯旧思而来新知。舍谬说而服旨诀。恐惧悱愤。恒交切于中。而未信苟从。亦非所以相待之本意也。仍欲权行倚阁。去读诸经。以俟义理之浃洽。知见之洒脱。然后徐复起意而思此。参较之久。庶冀其有究竟了断底时节矣。今年早春。余访先生于银山斋居。夜间先生叮咛曰子所撰中庸支节之图。规模广大。位置齐整。决知其可传于来后。而独第一大支之讼。尚未有勘处。子盍更思之。余辞谢。且告之以当优柔咀嚼。期于合盛见而乃已。及归平心顺气。积屡昕夕而反覆之。其于名义之左右者。若有是非之了然于胸中者。而取舍之定。毕竟是熟处难忘而已矣。盖以为中和中庸。固不甚相远。而今既统合诸章。另锡一名。则当取其指尤大意尤广该精粗兼本末。内外始终无所不包者而言之。不必胶固于先后之定局。拘碍于支节之异样。抑且就其次而执守之耳。中和固为首章矣。固已尽性情之德矣。然较诸中庸。犹欠一庸字。中庸之中。已兼中和之义。而庸又是平常之谓也。则其指大而意广者。当在此而不在彼矣。且中而不庸则众人之一时未发。不足以位天地。和而不庸则喜怒之一事中节。不足以育万物。必其推而极之。以至于常久而不已。然后方可以语位育之功矣。苟其或断或续若存若亡。则日月至焉。只得为在外之宾而已。然则其旨义之着切吃紧。亦当归重于多一庸字地矣。积十章而为一支者。初无异于积卅章而为一篇。其为卅章之大指者。反不能为十章之大指乎。则孟公绰之优于赵魏老。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者是欤。其为一编之总名者。犹不嫌为一节之总名乎。则
免据宿见裁胸臆而画一本以投呈。忙里之错。分外之僭。固自知其不容逭矣。伊后因洲上指教。改学达为笃恭大支。南黎则所争殆二三而一再烂漫。并次第印可。独第一大支之中庸二字。坚欲易之以中和。书相订面相难。盖已十许番于四三载之间矣。先生之为末学用血诚龂龂而不欲已者。亦已辛且苦矣。然而瞽见执迷。钝根难拔。不能濯旧思而来新知。舍谬说而服旨诀。恐惧悱愤。恒交切于中。而未信苟从。亦非所以相待之本意也。仍欲权行倚阁。去读诸经。以俟义理之浃洽。知见之洒脱。然后徐复起意而思此。参较之久。庶冀其有究竟了断底时节矣。今年早春。余访先生于银山斋居。夜间先生叮咛曰子所撰中庸支节之图。规模广大。位置齐整。决知其可传于来后。而独第一大支之讼。尚未有勘处。子盍更思之。余辞谢。且告之以当优柔咀嚼。期于合盛见而乃已。及归平心顺气。积屡昕夕而反覆之。其于名义之左右者。若有是非之了然于胸中者。而取舍之定。毕竟是熟处难忘而已矣。盖以为中和中庸。固不甚相远。而今既统合诸章。另锡一名。则当取其指尤大意尤广该精粗兼本末。内外始终无所不包者而言之。不必胶固于先后之定局。拘碍于支节之异样。抑且就其次而执守之耳。中和固为首章矣。固已尽性情之德矣。然较诸中庸。犹欠一庸字。中庸之中。已兼中和之义。而庸又是平常之谓也。则其指大而意广者。当在此而不在彼矣。且中而不庸则众人之一时未发。不足以位天地。和而不庸则喜怒之一事中节。不足以育万物。必其推而极之。以至于常久而不已。然后方可以语位育之功矣。苟其或断或续若存若亡。则日月至焉。只得为在外之宾而已。然则其旨义之着切吃紧。亦当归重于多一庸字地矣。积十章而为一支者。初无异于积卅章而为一篇。其为卅章之大指者。反不能为十章之大指乎。则孟公绰之优于赵魏老。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者是欤。其为一编之总名者。犹不嫌为一节之总名乎。则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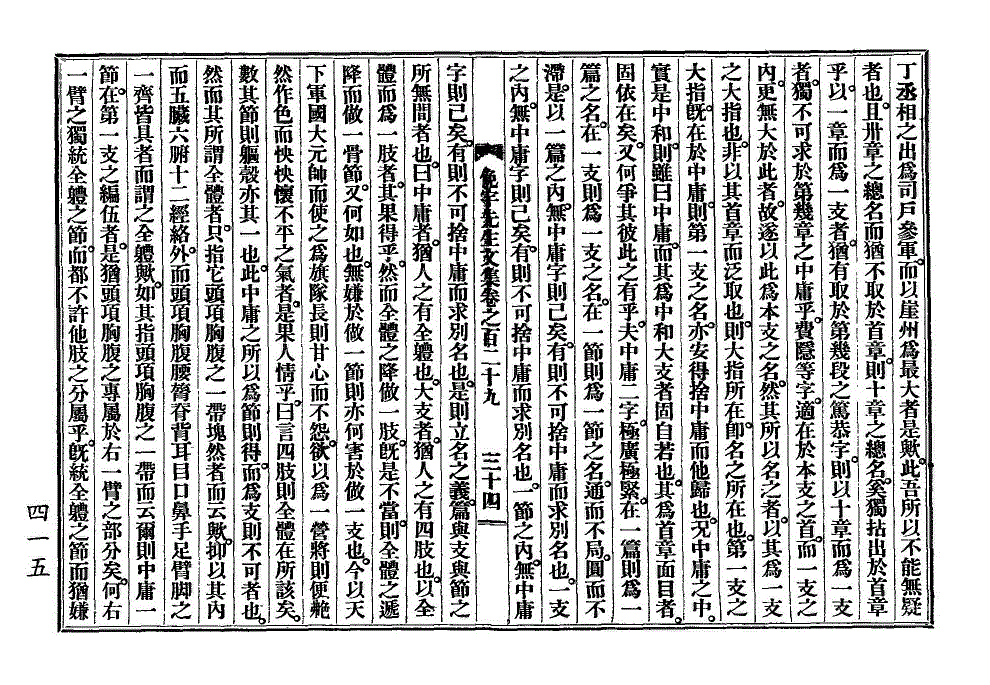 丁丞相之出为司户参军。而以崖州为最大者是欤。此吾所以不能无疑者也。且卅章之总名而犹不取于首章。则十章之总名。奚独拈出于首章乎。以一章而为一支者。犹有取于第几段之笃恭字。则以十章而为一支者。独不可求于第几章之中庸乎。费隐等字。适在于本支之首。而一支之内。更无大于此者。故遂以此为本支之名。然其所以名之者。以其为一支之大指也。非以其首章而泛取也。则大指所在。即名之所在也。第一支之大指。既在于中庸。则第一支之名。亦安得舍中庸而他归也。况中庸之中。实是中和。则虽曰中庸。而其为中和大支者固自若也。其为首章面目者。固依在矣。又何争其彼此之有乎。夫中庸二字。极广极紧。在一篇则为一篇之名。在一支则为一支之名。在一节则为一节之名。通而不局。圆而不滞。是以一篇之内。无中庸字则已矣。有则不可舍中庸而求别名也。一支之内。无中庸字则已矣。有则不可舍中庸而求别名也。一节之内。无中庸字则已矣。有则不可舍中庸而求别名也。是则立名之义。篇与支与节之所无间者也。曰中庸者。犹人之有全体也。大支者。犹人之有四肢也。以全体而为一肢者。其果得乎。然而全体之降做一肢。既是不当。则全体之递降而做一骨节。又何如也。无嫌于做一节则亦何害于做一支也。今以天下军国大元帅而使之为旗队长则甘心而不怨。欲以为一营将则便艴然作色而怏怏怀不平之气者。是果人情乎。曰言四肢则全体在所该矣。数其节则躯壳亦其一也。此中庸之所以为节则得。而为支则不可者也。然而其所谓全体者。只指它头项胸腹之一带块然者而云欤。抑以其内而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外而头项胸腹腰膂脊背耳目口鼻手足臂脚之一齐皆具者而谓之全体欤。如其指头项胸腹之一带而云尔则中庸一节。在第一支之编伍者。是犹头项胸腹之专属于右一臂之部分矣。何右一臂之独统全体之节。而都不许他肢之分属乎。既统全体之节而犹嫌
丁丞相之出为司户参军。而以崖州为最大者是欤。此吾所以不能无疑者也。且卅章之总名而犹不取于首章。则十章之总名。奚独拈出于首章乎。以一章而为一支者。犹有取于第几段之笃恭字。则以十章而为一支者。独不可求于第几章之中庸乎。费隐等字。适在于本支之首。而一支之内。更无大于此者。故遂以此为本支之名。然其所以名之者。以其为一支之大指也。非以其首章而泛取也。则大指所在。即名之所在也。第一支之大指。既在于中庸。则第一支之名。亦安得舍中庸而他归也。况中庸之中。实是中和。则虽曰中庸。而其为中和大支者固自若也。其为首章面目者。固依在矣。又何争其彼此之有乎。夫中庸二字。极广极紧。在一篇则为一篇之名。在一支则为一支之名。在一节则为一节之名。通而不局。圆而不滞。是以一篇之内。无中庸字则已矣。有则不可舍中庸而求别名也。一支之内。无中庸字则已矣。有则不可舍中庸而求别名也。一节之内。无中庸字则已矣。有则不可舍中庸而求别名也。是则立名之义。篇与支与节之所无间者也。曰中庸者。犹人之有全体也。大支者。犹人之有四肢也。以全体而为一肢者。其果得乎。然而全体之降做一肢。既是不当。则全体之递降而做一骨节。又何如也。无嫌于做一节则亦何害于做一支也。今以天下军国大元帅而使之为旗队长则甘心而不怨。欲以为一营将则便艴然作色而怏怏怀不平之气者。是果人情乎。曰言四肢则全体在所该矣。数其节则躯壳亦其一也。此中庸之所以为节则得。而为支则不可者也。然而其所谓全体者。只指它头项胸腹之一带块然者而云欤。抑以其内而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外而头项胸腹腰膂脊背耳目口鼻手足臂脚之一齐皆具者而谓之全体欤。如其指头项胸腹之一带而云尔则中庸一节。在第一支之编伍者。是犹头项胸腹之专属于右一臂之部分矣。何右一臂之独统全体之节。而都不许他肢之分属乎。既统全体之节而犹嫌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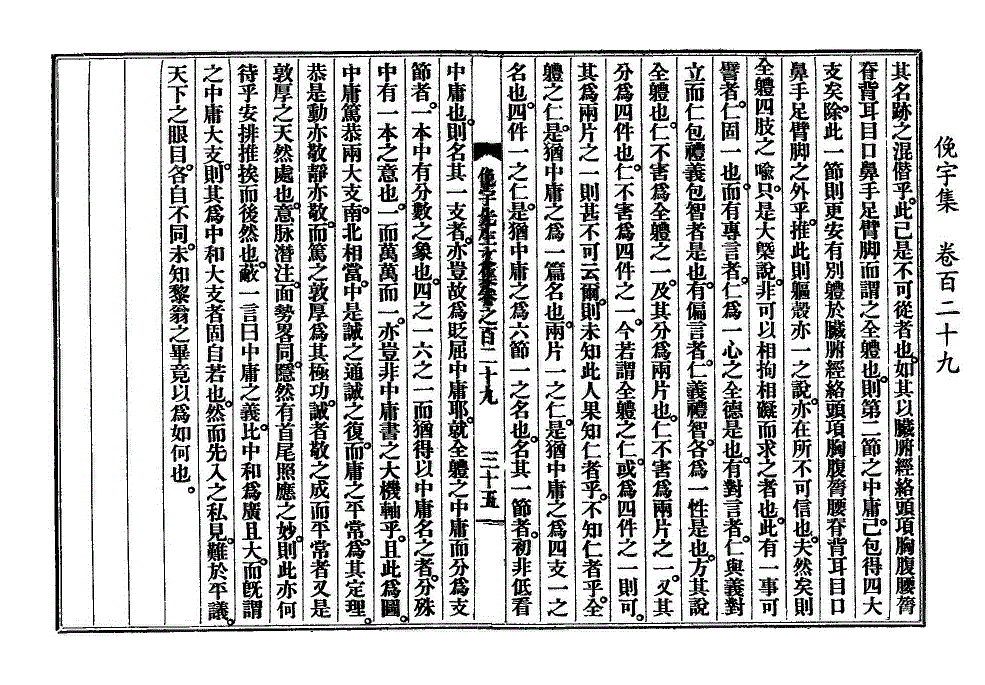 其名迹之混僭乎。此已是不可从者也。如其以脏腑经络头项胸腹腰膂脊背耳目口鼻手足臂脚而谓之全体也。则第二节之中庸。已包得四大支矣。除此一节则更安有别体于脏腑经络头项胸腹膂腰(腰膂)脊背耳目口鼻手足臂脚之外乎。推此则躯壳亦一之说。亦在所不可信也。夫然矣则全体四肢之喻。只是大既说。非可以相拘相碍而求之者也。此有一事可譬者。仁固一也。而有专言者。仁为一心之全德是也。有对言者。仁与义对立而仁包礼义包智者是也。有偏言者。仁义礼智。各为一性是也。方其说全体也。仁不害为全体之一。及其分为两片也。仁不害为两片之一。又其分为四件也。仁不害为四件之一。今若谓全体之仁。或为四件之一则可。其为两片之一则甚不可云尔。则未知此人果知仁者乎。不知仁者乎。全体之仁。是犹中庸之为一篇名也。两片一之仁。是犹中庸之为四支一之名也。四件一之仁。是犹中庸之为六节一之名也。名其一节者。初非低看中庸也。则名其一支者。亦岂故为贬屈中庸耶。就全体之中庸而分为支节者。一本中有分数之象也。四之一六之一而犹得以中庸名之者。分殊中有一本之意也。一而万万而一。亦岂非中庸书之大机轴乎。且此为图。中庸笃恭两大支。南北相当。中是诚之通诚之复。而庸之平常。为其定理。恭是动亦敬静亦敬。而笃之敦厚为其极功。诚者敬之成而平常者又是敦厚之天然处也。意脉潜注。面势略同。隐然有首尾照应之妙。则此亦何待乎安排推挨而后然也。蔽一言曰中庸之义。比中和为广且大。而既谓之中庸大支。则其为中和大支者固自若也。然而先入之私见。难于平议。天下之眼目。各自不同。未知黎翁之毕竟以为如何也。
其名迹之混僭乎。此已是不可从者也。如其以脏腑经络头项胸腹腰膂脊背耳目口鼻手足臂脚而谓之全体也。则第二节之中庸。已包得四大支矣。除此一节则更安有别体于脏腑经络头项胸腹膂腰(腰膂)脊背耳目口鼻手足臂脚之外乎。推此则躯壳亦一之说。亦在所不可信也。夫然矣则全体四肢之喻。只是大既说。非可以相拘相碍而求之者也。此有一事可譬者。仁固一也。而有专言者。仁为一心之全德是也。有对言者。仁与义对立而仁包礼义包智者是也。有偏言者。仁义礼智。各为一性是也。方其说全体也。仁不害为全体之一。及其分为两片也。仁不害为两片之一。又其分为四件也。仁不害为四件之一。今若谓全体之仁。或为四件之一则可。其为两片之一则甚不可云尔。则未知此人果知仁者乎。不知仁者乎。全体之仁。是犹中庸之为一篇名也。两片一之仁。是犹中庸之为四支一之名也。四件一之仁。是犹中庸之为六节一之名也。名其一节者。初非低看中庸也。则名其一支者。亦岂故为贬屈中庸耶。就全体之中庸而分为支节者。一本中有分数之象也。四之一六之一而犹得以中庸名之者。分殊中有一本之意也。一而万万而一。亦岂非中庸书之大机轴乎。且此为图。中庸笃恭两大支。南北相当。中是诚之通诚之复。而庸之平常。为其定理。恭是动亦敬静亦敬。而笃之敦厚为其极功。诚者敬之成而平常者又是敦厚之天然处也。意脉潜注。面势略同。隐然有首尾照应之妙。则此亦何待乎安排推挨而后然也。蔽一言曰中庸之义。比中和为广且大。而既谓之中庸大支。则其为中和大支者固自若也。然而先入之私见。难于平议。天下之眼目。各自不同。未知黎翁之毕竟以为如何也。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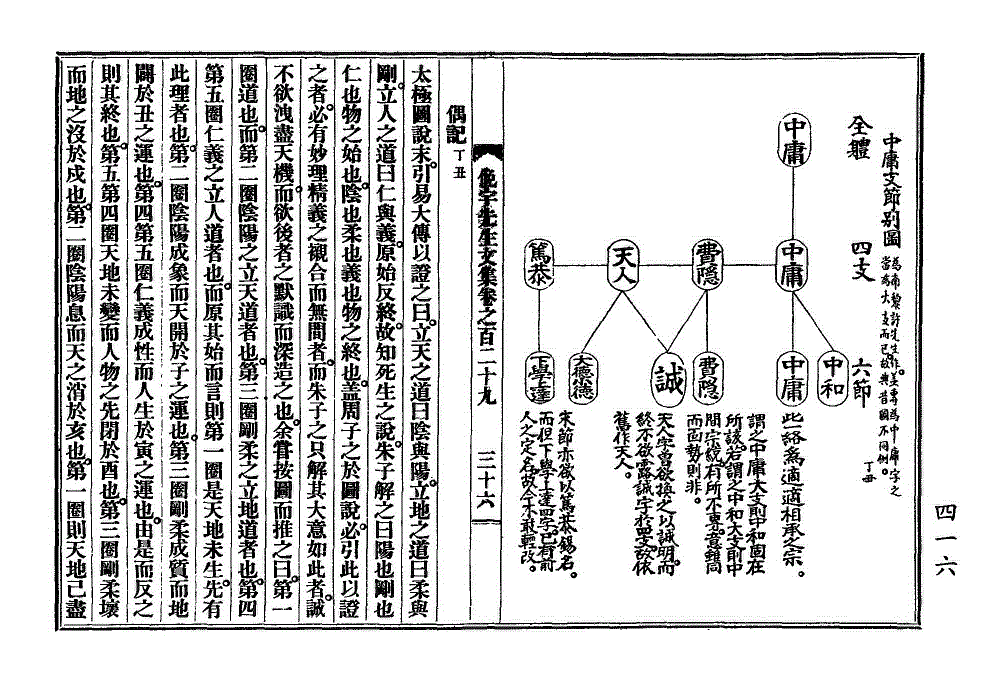 中庸支节别图(为南黎许先生作。盖专为中庸字之当为大支而已。故与昔图不同例。○丁丑。)
中庸支节别图(为南黎许先生作。盖专为中庸字之当为大支而已。故与昔图不同例。○丁丑。)삽화 새창열기
偶记(丁丑)
太极图说末。引易大传以證之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朱子解之曰阳也刚也仁也物之始也。阴也柔也义也物之终也。盖周子之于图说。必引此以證之者。必有妙理精义之衬合而无间者。而朱子之只解其大意如此者。诚不欲泄尽天机。而欲后者之默识而深造之也。余尝按图而推之曰。第一圈道也。而第二圈阴阳之立天道者也。第三圈刚柔之立地道者也。第四第五圈仁义之立人道者也。而原其始而言则第一圈是天地未生。先有此理者也。第二圈阴阳成象而天开于子之运也。第三圈刚柔成质而地辟于丑之运也。第四第五圈仁义成性而人生于寅之运也。由是而反之则其终也。第五第四圈天地未变而人物之先闭于酉也。第三圈刚柔坏而地之没于戌也。第二圈阴阳息而天之消于亥也。第一圈则天地已尽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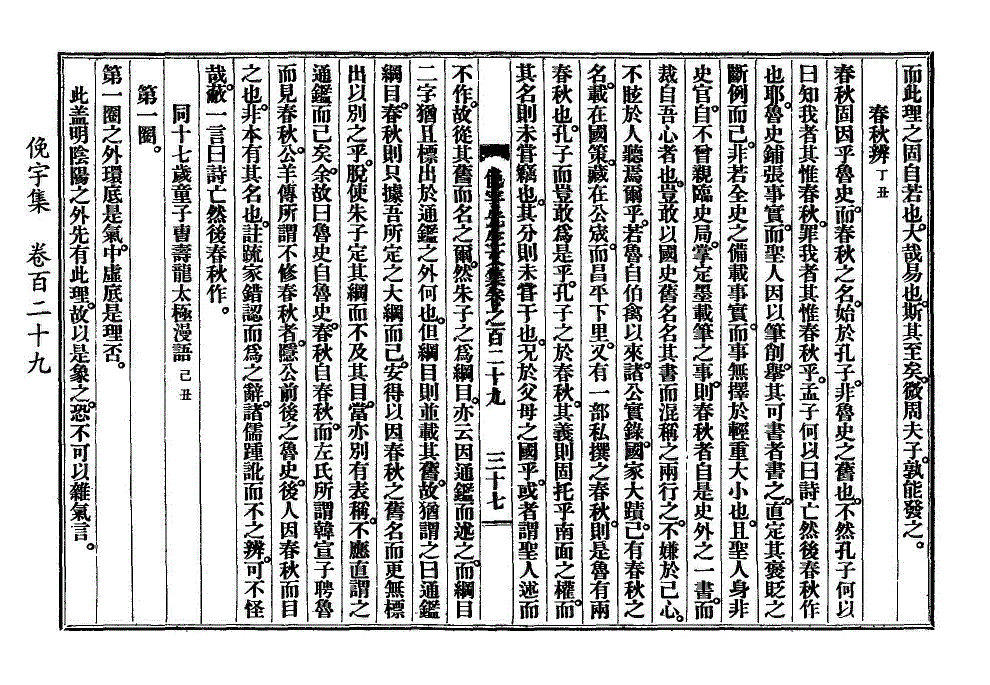 而此理之固自若也。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微周夫子。孰能发之。
而此理之固自若也。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微周夫子。孰能发之。春秋辨(丁丑)
春秋固因乎鲁史。而春秋之名。始于孔子。非鲁史之旧也。不然孔子何以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何以曰诗亡然后春秋作也耶。鲁史铺张事实。而圣人因以笔削。举其可书者书之。直定其褒贬之断例而已。非若全史之备载事实。而事无择于轻重大小也。且圣人身非史官。自不曾亲临史局。掌定墨载笔之事。则春秋者自是史外之一书。而裁自吾心者也。岂敢以国史旧名名其书而混称之两行之。不嫌于己心。不眩于人听焉尔乎。若鲁自伯禽以来。诸公实录。国家大迹。已有春秋之名。载在国策。藏在公宬。而昌平下里。又有一部私撰之春秋。则是鲁有两春秋也。孔子而岂敢为是乎。孔子之于春秋。其义则固托乎南面之权。而其名则未尝窃也。其分则未尝于也。况于父母之国乎。或者谓圣人述而不作。故从其旧而名之尔。然朱子之为纲目。亦云因通鉴而述之。而纲目二字犹且标出于通鉴之外何也。但纲目则并载其旧。故犹谓之曰通鉴纲目。春秋则只据吾所定之大纲而已。安得以因春秋之旧名而更无标出以别之乎。脱使朱子定其纲而不及其目。当亦别有表称。不应直谓之通鉴而已矣。余故曰鲁史自鲁史。春秋自春秋。而左氏所谓韩宣子聘鲁而见春秋。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者。隐公前后之鲁史。后人因春秋而目之也。非本有其名也。注疏家错认而为之辞。诸儒踵讹而不之辨。可不怪哉。蔽一言曰诗亡然后春秋作。
同十七岁童子曹寿龙太极漫语(己丑)
第一圈。
第一圈之外环底是气。中虚底是理否。
此盖明阴阳之外先有此理。故以是象之。恐不可以杂气言。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7L 页
 此说甚善。但之外二字做病。改以未生二字如何。
此说甚善。但之外二字做病。改以未生二字如何。如此说尤好。
盖此圈是单指理底。外圆者状此理之无方也。中虚者状此理之无形也。于此不可径论气。而世或以墨画之周于外者。疑其为有形之气。然苟以此理之无形而都不着墨画。则其为状理者安在哉。况只任纸面之虚白以为此理之状。则理不几于空荡荡者乎。
无方无形之说。大破迷惑。
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更无两样。而周子之图圆而为○。朱子于易总之极乃横而为
图以造化言。造化无方故圆。易以卦爻言。卦爻有位故横。其理则初非有别也。
所论得之矣。此理之妙。玲珑活络。随其所看而无所不通。以其自在而浑然者看则太极可圆而为○。以其各具而截然者看则太极可方而为
天地万物之生。其方圆竖倒之不齐者。实由气之流行。或升或降或飞或潜。吹万不一。而其理则未尝不同。故凡物莫不有是性耳。今以太极之体。谓有方圆竖倒之殊。则似以理为局一之物。不审如何。
以其或方或圆或竖或横或倒。故谓之理通。若方而不能圆。圆而不能竖。竖而不能横且倒焉。则其局甚矣。安得谓之理通乎。且道若无升底理。气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8H 页
 何能自升。若无降底理。气何能自降。若无飞底潜底理。气何能自飞自潜。且道若无圆底理。圆底物从何以生。若无方底理。方底物从何以生。若无竖底横底倒底理。竖底横底倒底物。从何以生。
何能自升。若无降底理。气何能自降。若无飞底潜底理。气何能自飞自潜。且道若无圆底理。圆底物从何以生。若无方底理。方底物从何以生。若无竖底横底倒底理。竖底横底倒底物。从何以生。若谓有是理故有是气则闻命矣。其所以浑然者为天。截然者为地则可。若其流行者竖焉而为人。对待反本者横倒焉而为禽兽草木者何也。
理有自上而直下来底曰流行。人得其流行之正。故头向上而足向下。理有分殊而并行底曰对待。禽兽得其对待之偏。故头尾横立而齐平。理有自下而上达底曰反本。草木得其反本之专。故头向下而末向上。然此就其所重者言之耳。非谓在人阙对待上达之理。在物阙流行之理也。浑然截然。亦非独存于天地而无与于人物也。
人之得其正。禽兽草木之得其偏专之不同何欤。
理非有意于为天为地为人物也。只是混圆活动。自然而然矣。而于其自然之中。随所遇而生出个许多般底。譬如雨之播空。初非有意于大铃小铃。而及其得之者。有略略沾得一两点者。有通身沾透者。有圆底沾痕。有直底沾痕。有斜底沾痕。此皆自然而然。随所遇而成形底。非意之而为此者也。
理者混融贯通。无精粗无内外无上下无本末。其所以流行者对待者自下而上达者。气而已。若以人物所得之理。谓有偏正之殊。则是理有精粗内外上下本末之不同耳。且草木得反本之专而其蔽厚。禽兽得对待之偏而其蔽薄者何也。抑气之所蔽。不以理之多少而有间欤。
气则于其精也更无所谓粗底。于其粗也更无所谓精底。理则语其精而不遗乎粗。语其粗而不外乎精。内外上下本末。莫不皆然。是以气之流也流而已。更无所谓对立者。气之上也上而已。更无所谓直下底。惟理则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8L 页
 然。流行之中自有对待之妙。上达之处实有直下之妙。若其人物之所得者则理一之分殊者也。分殊与理一。初非二物。则不可以此而谓理有精粗内外上下本末也。草木则得其反本之专。故其气逆而塞。禽兽则得其对待之偏。故其气罅而开。此亦理之自然也。且道今将所以流行对待上达者。谓之气而已者可乎。须看所以字。不可胡说。
然。流行之中自有对待之妙。上达之处实有直下之妙。若其人物之所得者则理一之分殊者也。分殊与理一。初非二物。则不可以此而谓理有精粗内外上下本末也。草木则得其反本之专。故其气逆而塞。禽兽则得其对待之偏。故其气罅而开。此亦理之自然也。且道今将所以流行对待上达者。谓之气而已者可乎。须看所以字。不可胡说。自然所以之理。既闻命矣。盖自太极之本体言之。初无所谓气者。而阴阳未生之前。太极有何安着处乎。朱子以未发之体湛然虚明谓之太极。则湛然虚明之体。无气可资而能乎。或者谓第一圈之太极。为不杂于气。第二圈之中虚。为不离于气。此说恐有病。
俄所论既已契合。则循此而下。可以次而顺矣。太极本体。不以有气而加增。不以无气而欠缩。虽在今日腾倒之中。而本体自本体也。虽在极本穷源之时。而其本体亦无异于今日也。太极顾何尝独立而悬空哉。但从气而看则气有生灭。不是将既灭之气。复为方生之气焉。则自其才灭之际而言之。气有息而理自在。故气便根之以生生矣。苟如是则理之安著。又何须于气乎。特其气灭气生。间不容发。才有理便有气。才有气理便乘搭。故古人说理。必曰理寓于气。然极究其实相则理之无形。何寄着之足云乎。湛然虚明之体。亦非有资于气也。但气之清则透露而无所碍。故人之见之者。疑其气有所加欠于理也。一圈二圈之以不杂不离分者。徙涉破碎。非理之本色。盖不离不杂。即其一时一处而言耳。岂层节之可分乎。有病之云甚当。
阴阳未生之前。太极之体寂然不动。则是阴之理耶。
阴阳未生。是指前气才屈。新气未至之时而言矣。则方是时也。理搭于死气之上。此则动之理根于静。而是静也已属前天地。故自此天地言之则动为始而阳为先矣。既动而阳矣。静之理便根于动。而阴之理乃可言矣。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九 第 419H 页
 但自其太极之该蕴者而观之则为阳为阴之理。一时具有。自其太极之流行者而观之则动底理为先而为阳。静底理为后而为阴。是又观理之活法也。
但自其太极之该蕴者而观之则为阳为阴之理。一时具有。自其太极之流行者而观之则动底理为先而为阳。静底理为后而为阴。是又观理之活法也。第一圈所以无方无形者。盖象无极之意。则其太极之体。于何可见。若以无极直谓太极则可。若谓虽无极而实太极则似无分界了。
无极即太极也则分界不须论。特其立言之妙。略有分界耳。极者标准之名也。无极而太极。犹言无标准而大标准也。勉斋所谓无形而至形。无方而大方者此也。盖太极无形状。而天下之有形状者。莫不以此为根柢。太极无方所。而天下之有方所者。莫不以此为枢纽。无形之形。形之至也。而非若有形之局于一物也。无方之方。方之大也。而非若有方之滞于一隅也。即此无极而便可见太极之妙。非于无极之外。别求所谓太极也。
朱子以心为太极则是统言天之心耶。若统言天之心则亦合理气。
心为太极者。以心之本体妙用而言也。在天在人。初无两样。盖心之一字。地位甚阔。有统体本体偏体当体之殊。合理气统体也。单指理本体也。气之清浊偏体也。质之窍圆当体也。彼清浊而窍圆者。心之舆卫宅舍也。君子有不心者焉。惟合理气之说。最为完备。然所贵乎心者。以其能主宰万化也。以其有本然之良心也。是以前圣贤言心。多直指本体。孟子所谓良心本心仁义之心。程子所谓心则性及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朱子所谓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及心固是主宰底。所谓主宰底即此理者。皆是也。是皆心为太极之义也。言太极而太极不离乎阴阳。言本心而本心不离乎气质。不可以其不离之故而遂兼阴阳做太极。和气质做本心也。天之为积气而显然可见者。朱子犹常曰天即理也。况天之心。是单指主宰之帝者乎。若兼气而为主宰则是国有二君。家有二夫。天有二帝。人有二心。乌在其本体之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