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x 页
大溪遗稿卷之五
序
序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4H 页
 寿荷泉金相公序
寿荷泉金相公序传曰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朋友长幼所以参五伦而不可苟合者也。其在末俗。专以炎凉为交道者无足言。或耐久之地。小不协意。渐生猜阻。苦乐之际。视若迈迈者。君子病之。病之莫若反之圣训。未合也审其可合之人。已合也思其久合之道焉耳。前弘文提学荷泉金相公。文章冠朝野。德望著家国。六载劳勚。覃及全岭。实今之贤大夫也。吾大人之宦游泮邸也。以公家为所主。在英以屡世之好。尝谒而事之。半千里如一室。半百年如一日。斯盖近世未易有也。相公初度节。在仲冬下浣。奉大夫人柳氏设宴上寿。柳氏时年八十二。子婿诸孙俱显于 朝。国人称之。但去冬相公之自唐岳未返也。以不得如刘元城之居谪奉母为恨。今当此日。以老莱斑斓之衣。供悦左右。相公之感戴 天恩果何如哉。宗族宾僚孰不造门同庆。独吾大人晚暮家食。只悬旧日之想。在英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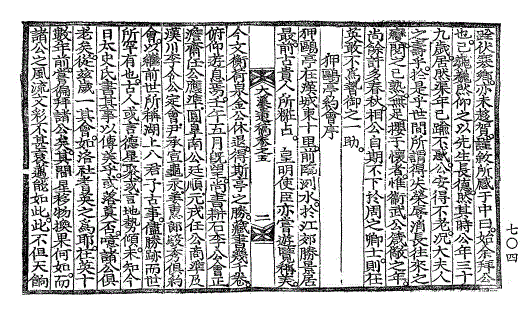 跧伏寒乡。亦未趍贺。谨叙所感于中曰。始余拜公也。已巍巍然仰之以先生长德。然其时公年三十九岁。居然渠年已踰不惑。公安得不老。况大夫人之寿乎。于是乎世间所谓得失荣辱消长往来之变。阅之已熟。无足撄于怀者。惟卫武公箴儆之年。尚馀许多春秋。相公自期。不下于周之卿士。则在英敢不为亵御之一助。
跧伏寒乡。亦未趍贺。谨叙所感于中曰。始余拜公也。已巍巍然仰之以先生长德。然其时公年三十九岁。居然渠年已踰不惑。公安得不老。况大夫人之寿乎。于是乎世间所谓得失荣辱消长往来之变。阅之已熟。无足撄于怀者。惟卫武公箴儆之年。尚馀许多春秋。相公自期。不下于周之卿士。则在英敢不为亵御之一助。狎鸥亭约会序
狎鸥亭在汉城东十里。前临洌水。于江郊胜景居最。前古贵人所妆占。 皇明使臣亦尝游览称美。今文衡荷泉金公休退。得斯亭之胜。藏书几千卷。俯仰游息焉。壬午五月既望。尚书耕石李公会正,澹斋任公应准,圆皋南公廷顺,元戎任公商准及汉川李令公定会,尹承宣龟永,姜惠郎骏秀俱约会。以继前世所称湖上八君子古事。尽胜迹而世所罕有也。古人或言德星聚。或言地势倾。未知今日太史氏书其事以传美乎。或落莫否。噫诸公俱老矣。从玆岁一其会。如洛社耆英之为耶。在英十数年前。尝遍拜诸公矣。其间星移物换果何如。而诸公之风流文彩不甚衰迈能如此。此不但天饷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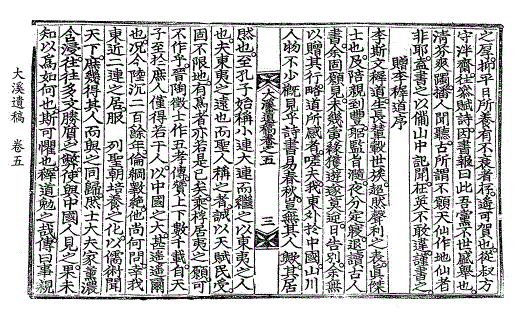 之厚。抑平日所养有不衰者存。遥可贺也。从叔方守泮斋。往参赋诗。因书报曰此吾党不世盛举也。清芬爽躅。播人闻听。古所谓不愿天仙作地仙者非耶。盍书之以备山中记闻。在英不敢违。谨书之。
之厚。抑平日所养有不衰者存。遥可贺也。从叔方守泮斋。往参赋诗。因书报曰此吾党不世盛举也。清芬爽躅。播人闻听。古所谓不愿天仙作地仙者非耶。盍书之以备山中记闻。在英不敢违。谨书之。赠李稚道序
李斯文稚道。生长辇毂世族。超然声利之表。真杰士也。及陪亲到丰。躬监旨瀡。夜分定寝。退读古人书。余固愿见。未几夤缘获游遂莫逆。日告别。余无以赠其行。略道所感者。嗟夫。我东外于中国。山川人物不少概见乎诗书易春秋。岂无其人欤。其居然也。至孔子始称小连大连而继之以东夷之人也。夫东夷之远也而圣人称之者。诚以天赋民受。固不限地。有为者亦若是已矣。乘桴居夷之愿。可不作乎。晋陶徵士作五孝传。赞上下数千载。自天子至于庶人仅得若干人。以中国之大。甚遥遥尔也。况今陆沉二百馀年。伦纲斁绝。他尚何问。幸我东近二连之居。服 列圣朝培养之化。以儒术闻天下。庶几得其人而与之同归。然士大夫家薰浓含浸。往往多文胜质之弊。使与中国人见之。果未知以为如何也。斯可惧也。稚道勉之哉。传曰事亲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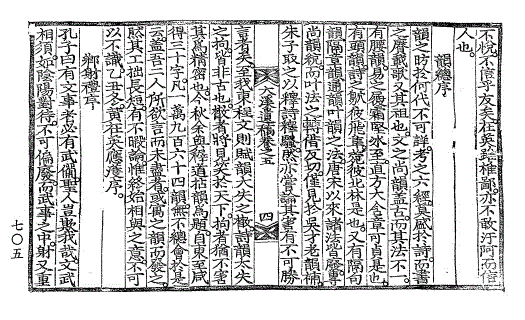 不悦。不信乎友矣。在英虽椎鄙。亦不敢污阿而信人也。
不悦。不信乎友矣。在英虽椎鄙。亦不敢污阿而信人也。韵总序
韵之昉于何代不可详。考之六经。莫盛于诗。而书之赓载歌又其祖也。文之尚韵盖古。而其法不一。有腰韵。易之履霜坚冰至。直方大含章可贞是也。有头韵。诗之鴥彼飞隼。菀彼北林是也。又有隔句韵,隔章韵,通韵叶韵之法。唐宋以来诸法皆废。专尚韵统。而叶法之转借反切。仅见于吴才老韵补。朱子取之以释诗释骚。然亦尝论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至我东程文则赋韵大失之散。诗韵太失之拘。皆非古也。散者将见笑于天下。拘者犹不害其为精密也。今秋余与稚道拈韵为题。自东至咸得三十字。凡一万九百六十四韵。无不总会于是云。盖吾二人所欲言而未尽者。或寓之韵而发之。然其工拙长短。有不暇论。惟终始相与之意。不可以不识。乙丑冬。黄在英应濩序。
乡射礼序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圣人岂欺我哉。文武相须。如阴阳对待。不可偏废。而武事之中。射又重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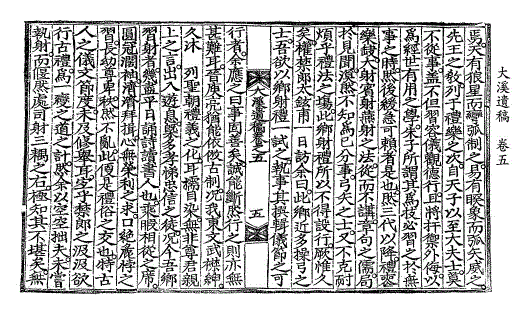 焉。天有狼星而弯弧制之。易有睽象而弧矢威之。先王之教。列于礼乐之次。自天子以至大夫士。莫不从事。盖不但习容仪观德行。且将捍御外侮。以为经世有用之学。朱子所谓其为技必习之于无事之时。然后缓急可赖者是也。然三代以降。礼丧乐缺。大射宾射燕射之法。从而不讲。章句之儒。局于见闻。漠然不知为己分事。弓矢之士。又不克耐烦乎礼法之场。此乡射礼所以不得设行。厥惟久矣。权禁郎太铉甫一日访余曰。此乡近多操弓之士。吾欲以乡射礼一试之。执事其撰辑仪节之可行者。余应之曰事固善矣。诚能断然行之则亦无甚难耳。晋庾亮犹能依仿古制。况我东文武襟绅。久沐 列圣朝礼义之化。耳擩目染。无非尊君亲上之言。出入游息。槩多孝悌忠信之徒。况今吾乡习射者。几尽平日诵诗读书人也。乘暇相从之席。圆冠阔袖。济济拜揖。心无荣利之求。口绝粗悖之习。长幼尊卑。秩然不乱。此便是礼俗之交也。特古人之仪文节度。未及修举耳。宜乎禁郎之汲汲欲行古礼。为一变之道之计。然余以空空拙夫。未尝执射。而偃然处司射三耦之右。极知其不堪矣。无
焉。天有狼星而弯弧制之。易有睽象而弧矢威之。先王之教。列于礼乐之次。自天子以至大夫士。莫不从事。盖不但习容仪观德行。且将捍御外侮。以为经世有用之学。朱子所谓其为技必习之于无事之时。然后缓急可赖者是也。然三代以降。礼丧乐缺。大射宾射燕射之法。从而不讲。章句之儒。局于见闻。漠然不知为己分事。弓矢之士。又不克耐烦乎礼法之场。此乡射礼所以不得设行。厥惟久矣。权禁郎太铉甫一日访余曰。此乡近多操弓之士。吾欲以乡射礼一试之。执事其撰辑仪节之可行者。余应之曰事固善矣。诚能断然行之则亦无甚难耳。晋庾亮犹能依仿古制。况我东文武襟绅。久沐 列圣朝礼义之化。耳擩目染。无非尊君亲上之言。出入游息。槩多孝悌忠信之徒。况今吾乡习射者。几尽平日诵诗读书人也。乘暇相从之席。圆冠阔袖。济济拜揖。心无荣利之求。口绝粗悖之习。长幼尊卑。秩然不乱。此便是礼俗之交也。特古人之仪文节度。未及修举耳。宜乎禁郎之汲汲欲行古礼。为一变之道之计。然余以空空拙夫。未尝执射。而偃然处司射三耦之右。极知其不堪矣。无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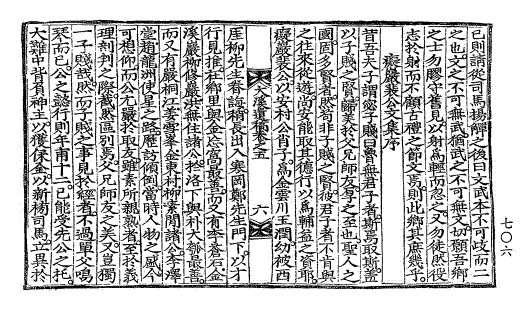 已则请从司马扬觯之后曰文武本不可歧而二之也。文之不可无武。犹武之不可无文。切愿吾乡之士勿胶守旧见。以射为轻而忽之。又勿徒然役志于射而不顾古礼之节文焉。则此乡其庶几乎。
已则请从司马扬觯之后曰文武本不可歧而二之也。文之不可无武。犹武之不可无文。切愿吾乡之士勿胶守旧见。以射为轻而忽之。又勿徒然役志于射而不顾古礼之节文焉。则此乡其庶几乎。痴岩裴公文集序
昔吾夫子谓宓子贱曰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盖以子贱之贤。归美于父兄师友。厚之至也。圣人之国。固多贤者。然苟非子贱之贤。彼君子者不肯与之往来从游。尚安能取其德行以为辅益之资耶。痴岩裴公。以安村公肖子。为金云川玉润。幼被西厓柳先生眷诲。稍长出入寒冈郑先生门下。以才行见推。在乡里与金忘窝最善。而又有李苍石,金溪岩,柳修岩,洪无住诸公。于洛下与朴大瓠最善。而又有严桐江,姜雪峰,金东村,柳素閒诸公。李泽堂,赵龙洲使星之路。历访倾倒。当时人物之盛。今可想仰。而公尤严于取友。虽素所亲熟者。至于义理剖判之际。截然区别焉。父兄师友之美。又岂独一子贱哉。然而子贱之事见于经者。不过单父鸣琴而已。公之懿行则年甫十二。已能受先公之托。大难中背负神主。以获保全。以新榜司马。立异于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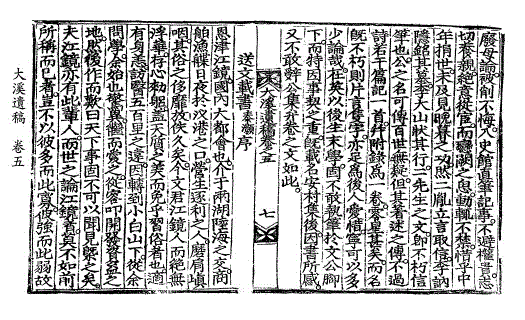 废母论。被削不悔。入史馆直笔记事。不避权贵。志切养亲。绝意从宦。而恋阙之思。动辄不禁。惜乎中年捐世。未及见晚暮之功。然二胤立言取信。李讷隐铭其墓。李大山状其行。二先生之文。即不朽信笔也。公之名可传百世无疑。但其著述之传。不过诗若干篇记一首。并附录为一卷。零星甚矣。而名既不朽则片言只字。亦足为后人爱惜。宁可以多少论哉。在英以后生末学。固不敢执笔于文公脚下。而特因事契之重。既载名安村集后。因书所感。又不敢辞公集弁卷之文如此。
废母论。被削不悔。入史馆直笔记事。不避权贵。志切养亲。绝意从宦。而恋阙之思。动辄不禁。惜乎中年捐世。未及见晚暮之功。然二胤立言取信。李讷隐铭其墓。李大山状其行。二先生之文。即不朽信笔也。公之名可传百世无疑。但其著述之传。不过诗若干篇记一首。并附录为一卷。零星甚矣。而名既不朽则片言只字。亦足为后人爱惜。宁可以多少论哉。在英以后生末学。固不敢执笔于文公脚下。而特因事契之重。既载名安村集后。因书所感。又不敢辞公集弁卷之文如此。送文载书(泰灏)序
恩津江镜。国内大都会也。介于两湖陆海之交。商舶渔艓日夜于汊港之口。营生逐利之人。磨肩填咽。其俗之侈靡放佚久矣。今文君江镜人而绝无浮华。存心敕躬。盖天质之美而免乎习俗者也。适有身恙。访医五百里之远。因转到小白山下。从余问学。余始也惊异。继而爱之。从容叩开发资益之地。然后作而叹曰天下事固不可以闻见槩之矣。夫江镜亦有此辈人。而世之论江镜者。莫不如前所称而已者。岂不以彼多而此寡。彼强而此弱故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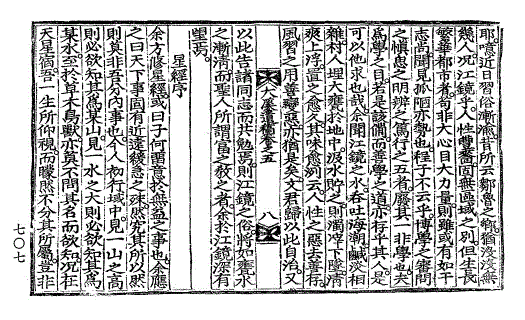 耶。噫近日习俗渐渝。昔所云邹鲁之乡。犹没没无几人。况江镜乎。人性丰啬。固无区域之别。但生长繁华都市者。苟非大心目大力量。则虽或有如干志尚。闻见孤陋亦势也。程子不云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夫为学之目。若是该备。而善学之道。亦存乎其人。是可以他求也哉。余闻江镜之水。吞吐海潮。咸淡相杂。村人埋大瓮于地中。汲水贮之。则浊滓下坠。清爽上浮。置之愈久。其味愈洌云。人性之恶去善存。风习之用善变恶。亦犹是矣。文君归以此自治。又以此告诸同志而共勉焉。则江镜之俗。将如瓮水之渐清。而圣人所谓富之教之者。余于江镜深有望焉。
耶。噫近日习俗渐渝。昔所云邹鲁之乡。犹没没无几人。况江镜乎。人性丰啬。固无区域之别。但生长繁华都市者。苟非大心目大力量。则虽或有如干志尚。闻见孤陋亦势也。程子不云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夫为学之目。若是该备。而善学之道。亦存乎其人。是可以他求也哉。余闻江镜之水。吞吐海潮。咸淡相杂。村人埋大瓮于地中。汲水贮之。则浊滓下坠。清爽上浮。置之愈久。其味愈洌云。人性之恶去善存。风习之用善变恶。亦犹是矣。文君归以此自治。又以此告诸同志而共勉焉。则江镜之俗。将如瓮水之渐清。而圣人所谓富之教之者。余于江镜深有望焉。星经序
余方修星经。或曰子何留意于无益之事也。余应之曰天下事固有近远缓急之殊。然究其所以然则莫非吾分内事也。今人初行域中。见一山之高则必欲知其为某山。见一水之大则必欲知其为某水。至于草木鸟兽。亦莫不问其名而欲知。况在天星宿。吾一生所仰视。而矇然不分其所属。岂非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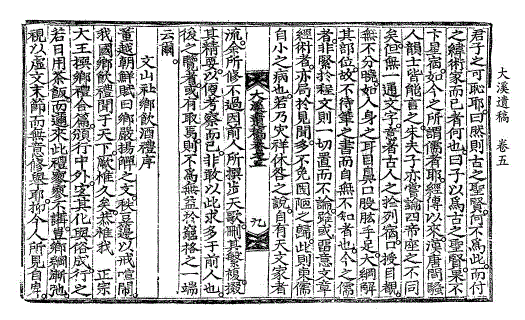 君子之可耻耶。曰然则古之圣贤。何不为此。而付之纬术家而已者何也。曰子以为古之圣贤。果不卞星宿。如今之所谓儒者耶。经传以来。汉唐间骚人韵士皆能言之。朱夫子亦尝论四帝座之不同矣。但无一通文字。意者古人之于列宿。口授目睹。无不分晓。如人身之耳目鼻口股肱手足。大纲解其部位。故不待笔之书而自无不知者也。今之儒者。非紧于程文则一切置而不论。虽或留意文章经术者。亦局于见闻。多不免固陋之归。此则东儒自小之病也。若乃灾祥休咎之说。自有天文家者流。余所修不过因前人所撰步天歌。删其繁复。掇其精要。以便考察而已。非敢以此求多于前人也。后之览者。或有取焉。则不为无益于穷格之一端云尔。
君子之可耻耶。曰然则古之圣贤。何不为此。而付之纬术家而已者何也。曰子以为古之圣贤。果不卞星宿。如今之所谓儒者耶。经传以来。汉唐间骚人韵士皆能言之。朱夫子亦尝论四帝座之不同矣。但无一通文字。意者古人之于列宿。口授目睹。无不分晓。如人身之耳目鼻口股肱手足。大纲解其部位。故不待笔之书而自无不知者也。今之儒者。非紧于程文则一切置而不论。虽或留意文章经术者。亦局于见闻。多不免固陋之归。此则东儒自小之病也。若乃灾祥休咎之说。自有天文家者流。余所修不过因前人所撰步天歌。删其繁复。掇其精要。以便考察而已。非敢以此求多于前人也。后之览者。或有取焉。则不为无益于穷格之一端云尔。文山社乡饮酒礼序
董越朝鲜赋曰乡严扬觯之文。秩豆笾以戒喧闹。我国乡饮礼闻于天下。厥惟久矣。恭惟我 正宗大王撰乡礼合篇。颁行中外。宜其化与俗成。行之若日用茶饭。而迩来此礼寥寥不讲。岂乡纲渐弛。视以虚文末节而无意修举耶。抑今人所见自卑。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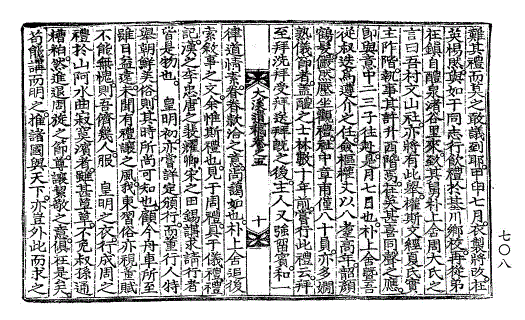 难其礼而莫之敢议到耶。甲申七月。衣制将改。在英惕然。与如干同志行饮礼于基川乡校。再从弟在镇自醴泉渚谷里来。致其舅朴上舍周大氏之言曰吾村文山社。亦将有此举。权斯文经夏氏实主阼阶。执事其许升西阶焉。在英甚喜同声之应。即与意中二三子往赴。是月七日也。朴上舍暨吾从叔迭为遵介之任。佥枢权丈以八耋高年。韶颜鹤发。俨然压坐观礼。社中章甫仅八十员。亦多娴熟仪节者。盖醴之士林数十年前。尝行此礼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后。主人又强留宾。和一律道情素。眷眷款洽之意。尚蔼如也。朴上舍追后索叙事之文。余惟斯礼也。见于周礼。具于仪礼,礼记。汉之李忠,唐之裴耀卿,宋之田锡讲求请行者皆是物也。 皇明初。亦尝详定颁行。而董行人特举朝鲜美俗。则其时所尚可知也。顾今舟车所至虽日益远。未闻有礼让之风。我东习俗亦视董赋不能无愧。则吾侪几人。服 皇明之衣。行成周之礼于山阿水曲寂寞滨者。虽甚草草。不免叔孙通糟粕。然进退周旋之节。尊让絜敬之意。俱在是矣。苟能讲而明之。推诸国与天下。亦岂外此而求之
难其礼而莫之敢议到耶。甲申七月。衣制将改。在英惕然。与如干同志行饮礼于基川乡校。再从弟在镇自醴泉渚谷里来。致其舅朴上舍周大氏之言曰吾村文山社。亦将有此举。权斯文经夏氏实主阼阶。执事其许升西阶焉。在英甚喜同声之应。即与意中二三子往赴。是月七日也。朴上舍暨吾从叔迭为遵介之任。佥枢权丈以八耋高年。韶颜鹤发。俨然压坐观礼。社中章甫仅八十员。亦多娴熟仪节者。盖醴之士林数十年前。尝行此礼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后。主人又强留宾。和一律道情素。眷眷款洽之意。尚蔼如也。朴上舍追后索叙事之文。余惟斯礼也。见于周礼。具于仪礼,礼记。汉之李忠,唐之裴耀卿,宋之田锡讲求请行者皆是物也。 皇明初。亦尝详定颁行。而董行人特举朝鲜美俗。则其时所尚可知也。顾今舟车所至虽日益远。未闻有礼让之风。我东习俗亦视董赋不能无愧。则吾侪几人。服 皇明之衣。行成周之礼于山阿水曲寂寞滨者。虽甚草草。不免叔孙通糟粕。然进退周旋之节。尊让絜敬之意。俱在是矣。苟能讲而明之。推诸国与天下。亦岂外此而求之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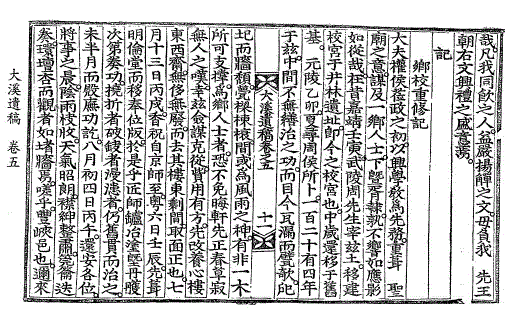 哉。凡我同饮之人。益严扬觯之文。毋负我 先王朝右文兴礼之盛意焉。
哉。凡我同饮之人。益严扬觯之文。毋负我 先王朝右文兴礼之盛意焉。大溪遗稿卷之五
记
乡校重修记
大夫权侯莅政之初。以兴学教为先务。重葺 圣庙之意。谋及一乡人士。下暨胥隶。孰不响如应影如从哉。在昔嘉靖壬寅。武陵周先生宰玆土。移建校宫于井林遗址。即今之校宫也。中岁还移于旧基。 元陵乙卯。更寻周侯所卜。一百二十有四年于玆。中间不无缮治之功。而目今瓦漏而甓欹。戺圮而墙颓。甍梁栋榱。间或为风雨之神。有非一木所可支撑。为乡人士者。恐不免晦轩先正春草寂无人之叹。幸玆佥谋克从。赀用有方。先改养心楼东西斋。无侈无废。而去其楼东剩间。取面正也。七月十三日丙戌。香祝自京师至。粤六日壬辰。先葺明伦堂而移奉位版。于是乎匠师垆冶涂塈丹雘次第奏功。挠折者破缺者漫漶者。仍旧贯而治之。未半月而殿庑功讫。八月初四日丙午。还安各位。将事之晨。阴雨快收。天气昭朗。襟绅整肃。筦籥迭奏。环坛杏而观者如堵墙焉。嗟乎。丰峡邑也。迩来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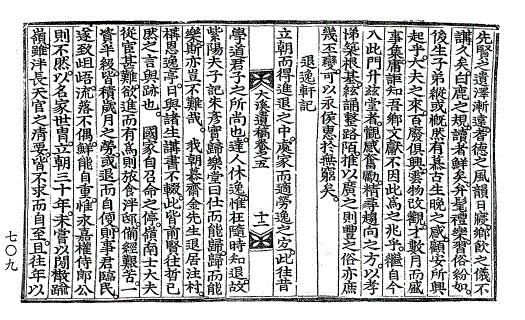 先贤之遗泽渐远。耆德之风韵日寝。乡饮之仪不讲久矣。白鹿之规。读者鲜矣。弁髦礼乐。习俗纷如。后生子弟纵或慨然有慕古生晚之感。顾安所兴起乎。大夫之来。百废俱兴。云物改观。才数月而盛事集。庸讵知吾乡文献不因此为之兆乎。继自今入此门升玆堂者。观感奋励。精寻趋向之方。以孝悌筑根基。弦诵整路陌。推以广之则丰之俗亦庶几丕变。可以永侯惠于无穷矣。
先贤之遗泽渐远。耆德之风韵日寝。乡饮之仪不讲久矣。白鹿之规。读者鲜矣。弁髦礼乐。习俗纷如。后生子弟纵或慨然有慕古生晚之感。顾安所兴起乎。大夫之来。百废俱兴。云物改观。才数月而盛事集。庸讵知吾乡文献不因此为之兆乎。继自今入此门升玆堂者。观感奋励。精寻趋向之方。以孝悌筑根基。弦诵整路陌。推以广之则丰之俗亦庶几丕变。可以永侯惠于无穷矣。退逸轩记
立朝而得进退之中。处家而适劳逸之宜。此往昔学道君子之所尚也。达人休逸。惟在随时知退。故紫阳夫子记朱彦实归乐堂曰仕而能归。归而能乐。斯亦岂不难哉。 我朝慕斋金先生退居注村。构恩逸亭。日与诸生讲书不辍。此皆前贤往哲已然之言与迹也。 国家自召命之停。岭南士大夫从宦甚难。欲进而有为则旅食泮邸。备经艰苦。一资半级。皆积岁月之劳。或退而自便。则事君临民。遂致龃龉。流落不偶。鲜能自重。惟永嘉权侍郎公则不然。以名家世胄。立朝三十年。未尝以閒散踰岭。虽泮长天官之清要。皆不求而自至。且往年以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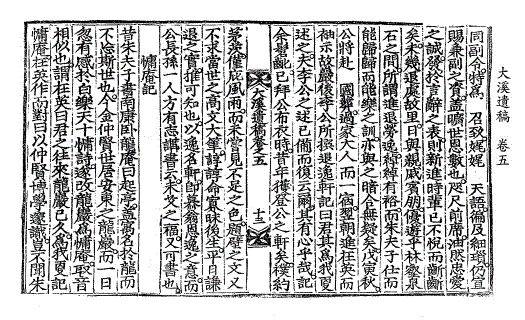 同副令。特为 召致。娓娓 天语。遍及细琐。仍宣赐兼副之资。盖旷世恩数也。咫尺前席。油然忠爱之诚。发于言辞之表。则新进时辈已不悦而龂龂矣。未几退处故里。日与亲戚宾朋。优游乎林壑泉石之间。所谓进退劳逸。绰绰有裕。而朱夫子仕而能归归而能乐之训。亦与之暗合无疑矣。戊寅秋。公将赴 国葬。过家大人而一宿。翌朝进在英而袖示故岩后李公所撰退逸轩记曰君其为我更述之。夫李公之述已备而复云尔。其有心乎哉。记余髫龀。已拜公布衣时。昔年获登公之轩矣。朴约茅茨。仅庇风雨。而未尝见不足之色。题壁之文又不求当世之高文大笔。谆谆命寡昧后生。平日谦退之实。推可知也。以逸名轩。即慕翁恩逸之意。而公长孙一人方有志讲书云。未艾之福。又可书也。
同副令。特为 召致。娓娓 天语。遍及细琐。仍宣赐兼副之资。盖旷世恩数也。咫尺前席。油然忠爱之诚。发于言辞之表。则新进时辈已不悦而龂龂矣。未几退处故里。日与亲戚宾朋。优游乎林壑泉石之间。所谓进退劳逸。绰绰有裕。而朱夫子仕而能归归而能乐之训。亦与之暗合无疑矣。戊寅秋。公将赴 国葬。过家大人而一宿。翌朝进在英而袖示故岩后李公所撰退逸轩记曰君其为我更述之。夫李公之述已备而复云尔。其有心乎哉。记余髫龀。已拜公布衣时。昔年获登公之轩矣。朴约茅茨。仅庇风雨。而未尝见不足之色。题壁之文又不求当世之高文大笔。谆谆命寡昧后生。平日谦退之实。推可知也。以逸名轩。即慕翁恩逸之意。而公长孙一人方有志讲书云。未艾之福。又可书也。慵庵记
昔朱夫子书南康卧龙庵曰起亭。盖寓名于龙而不忘斯世也。今金仲贤世居安东之龙岩。而一日忽有感于白乐天十慵诗。遂改龙岩为慵庵。取音相似也。谓在英曰君之往来龙岩已久。为我更记慵庵。在英作而对曰以仲贤博学邃识。岂不闻朱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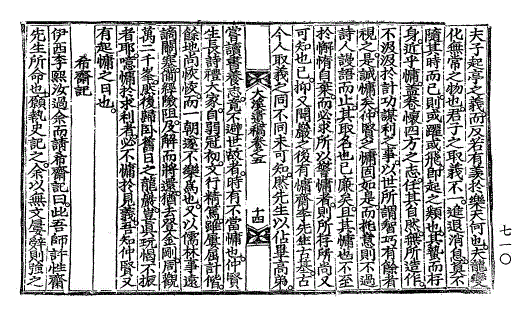 夫子起亭之义。而反若有羡于乐天何也。夫龙变化无常之物也。君子之取义不一。进退消息。莫不随其时而已。则或跃或飞。即起之类也。其蛰而存身。近乎慵。盖卷怀四方之志。任其自然。无所造作。不汲汲于计功谋利之事。以世所谓智巧有馀者视之。是诚慵矣。仲贤之慵固如是。而托意则不过诗人谩语而止。其取名也已廉矣。且其慵也不至于懈惰自弃。而必求所以警慵者。则所存所尚又可知也已。抑又闻岩之后有慵斋李先生古基。古今人取义之同不同未可知。然先生以佔毕高弟。尝读书养志。竟不避世故者。时有不当慵也。仲贤生长诗礼大家。自弱冠初。文行精笃。虽屡屈计偕。馀地尚恢恢。而一朝遂不乐为也。又以儒林事远谪关塞。备经险阻。及解而将还。犹去登金刚。周观万二千峰。然后归卧旧日之龙岩。岂真玩愒不振者耶。噫慵于求利者。必不慵于见义。吾知仲贤又有起慵之日也。
夫子起亭之义。而反若有羡于乐天何也。夫龙变化无常之物也。君子之取义不一。进退消息。莫不随其时而已。则或跃或飞。即起之类也。其蛰而存身。近乎慵。盖卷怀四方之志。任其自然。无所造作。不汲汲于计功谋利之事。以世所谓智巧有馀者视之。是诚慵矣。仲贤之慵固如是。而托意则不过诗人谩语而止。其取名也已廉矣。且其慵也不至于懈惰自弃。而必求所以警慵者。则所存所尚又可知也已。抑又闻岩之后有慵斋李先生古基。古今人取义之同不同未可知。然先生以佔毕高弟。尝读书养志。竟不避世故者。时有不当慵也。仲贤生长诗礼大家。自弱冠初。文行精笃。虽屡屈计偕。馀地尚恢恢。而一朝遂不乐为也。又以儒林事远谪关塞。备经险阻。及解而将还。犹去登金刚。周观万二千峰。然后归卧旧日之龙岩。岂真玩愒不振者耶。噫慵于求利者。必不慵于见义。吾知仲贤又有起慵之日也。希斋记
伊西李熙汝过余而请希斋记曰。此吾师许性斋先生所命也。愿执史记之。余以无文屡辞则强之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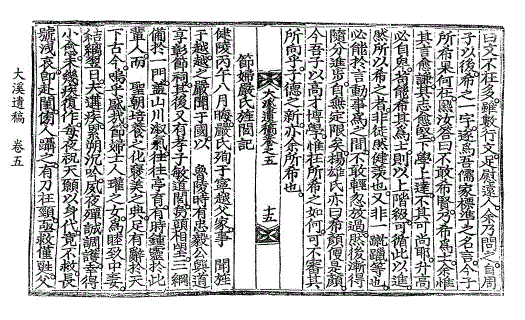 曰文不在多。虽数行文。足慰远人。余乃问之。自周子以后。希之一字。遂为吾儒家标准之名言。今子所希果何在。熙汝答曰不敢希贤。乃希为士。余惟其言愈谦。其志愈坚。下学上达。不其可尚耶。升高必自卑。苟能希其为士。则以上阶级。可循此以进。然所以希之者。非徒然健羡也。又非一蹴躐等也。必能于言动事为之间。不敢轻忽放过。然后渐得随分进步。自无定限矣。杨雄氏亦曰希颜便是颜。今吾子以高才博学。惟在所希之如何。可不审其所向乎。子德之新。亦余所希也。
曰文不在多。虽数行文。足慰远人。余乃问之。自周子以后。希之一字。遂为吾儒家标准之名言。今子所希果何在。熙汝答曰不敢希贤。乃希为士。余惟其言愈谦。其志愈坚。下学上达。不其可尚耶。升高必自卑。苟能希其为士。则以上阶级。可循此以进。然所以希之者。非徒然健羡也。又非一蹴躐等也。必能于言动事为之间。不敢轻忽放过。然后渐得随分进步。自无定限矣。杨雄氏亦曰希颜便是颜。今吾子以高才博学。惟在所希之如何。可不审其所向乎。子德之新。亦余所希也。节妇严氏旌闾记
健陵丙午八月晦。严氏殉于宁越父家。事 闻旌于越。越之严闻于国。以 鲁陵时有忠毅公兴道享彰节祠。其后又有孝子敏道闾。乌头相望。三纲备于一门。盖山川淑气。往往亭育。有时钟灵于此辈人。而 圣朝培养之化褒美之典。足有辞于天下古今。呜乎盛哉。节妇士人瓘之女。为睦致中妻。结缡翌日。夫遘疾。累朔沉吟。夙夜殚诚调护。幸得小愈。未几疾复作。每夜祝天愿以身代。竟不救。长号泄哀。即赴闺。傍人蹑之。有刀在颈。亟救仅苏。父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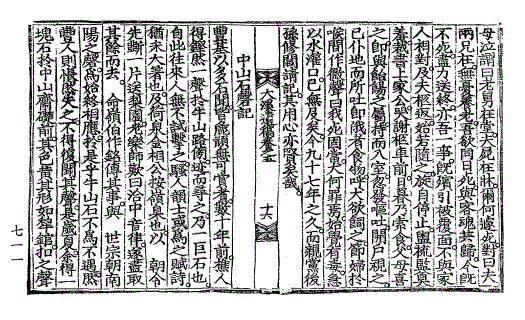 母泣谓曰老舅在堂。夫尸在床。尔何遽死。对曰夫两兄在。无忧养老。吾欲同日死。与客魂共归。今既不死。尽力送终。亦吾一事。既殡引被覆面。不与家人相对。及夫柩返。始若随之。旋自停止。盥梳监奠羞。裁书上家公。哭谢柩车前。日暮乃索食。父母喜之。即与饴饧之属。持而入室。忽发呕吐。开户视之。已仆地而所吐即俄者食物。呼犬欲饲之。节妇于喉间作微声曰我死固当。犬何罪焉。始觉有毒。急以水灌口。已无及矣。今九十七年之久。而亲党后孙修闾请记。其用心亦贤矣哉。
母泣谓曰老舅在堂。夫尸在床。尔何遽死。对曰夫两兄在。无忧养老。吾欲同日死。与客魂共归。今既不死。尽力送终。亦吾一事。既殡引被覆面。不与家人相对。及夫柩返。始若随之。旋自停止。盥梳监奠羞。裁书上家公。哭谢柩车前。日暮乃索食。父母喜之。即与饴饧之属。持而入室。忽发呕吐。开户视之。已仆地而所吐即俄者食物。呼犬欲饲之。节妇于喉间作微声曰我死固当。犬何罪焉。始觉有毒。急以水灌口。已无及矣。今九十七年之久。而亲党后孙修闾请记。其用心亦贤矣哉。中山石磬记
丰基以多石闻。皆粗顽无可赏者。数十年前。樵人得铿然一声于牛山路傍。迹而寻之。乃一巨石也。自此往来人无不试击之。骚人韵士或为之赋诗。犹未大著也。及荷泉金相公按岭臬也。以 朝令先斲一片送梨园。老乐师叹曰洽中音律。遂尽取其馀而去。 命岭伯作铭传其事。与 世宗朝南阳之磬。为始终相应。于是乎牛山石不为不遇。然丰人则怅然失之。不得复闻其声。是岁夏。余得一块石于中山斋础前。其色黄其形如犁錧。扣之声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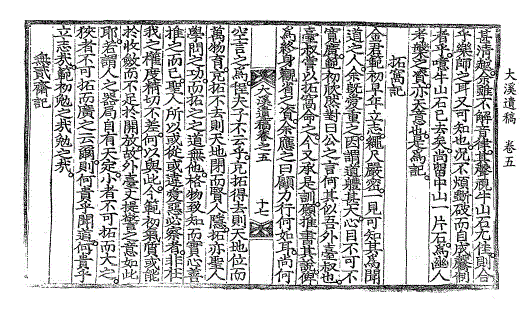 甚清越。余虽不解音律。其声视牛山石尤佳。则合乎乐师之耳又可知也。况不烦斲破而自成毊制者乎。噫牛山石已去矣。尚留中山一片石。为幽人考槃之资。亦天意也。是为记。
甚清越。余虽不解音律。其声视牛山石尤佳。则合乎乐师之耳又可知也。况不烦斲破而自成毊制者乎。噫牛山石已去矣。尚留中山一片石。为幽人考槃之资。亦天意也。是为记。拓窝记
金君范初早年立志。绳尺严密。一见可知其为闻道之人。余既爱重之。因谓道体甚大。心目不可不宽广。范初欣然对曰公之言何其似吾外台叔也。台叔尝以拓窝命之。今又承是训。愿推书其说。俾为终身观省之资。余应之曰顾力行何如耳。尚何空言之为。程夫子不云乎。充拓得去则天地位而万物育。充拓不去则天地闭而贤人隐。拓亦圣人学问之功。而拓之之道无他。格物致知而实心善推之而已。圣人所以或从或违爱恶必察者。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今范初气质或能于收敛而不足于开放。故外台丈提警之意如此耶。若谓人之器局自有天定。小者不可拓而大之。狭者不可拓而广之云尔。则何贵乎闻道。何贵乎立志哉。范初勉之哉勉之哉。
无贰斋记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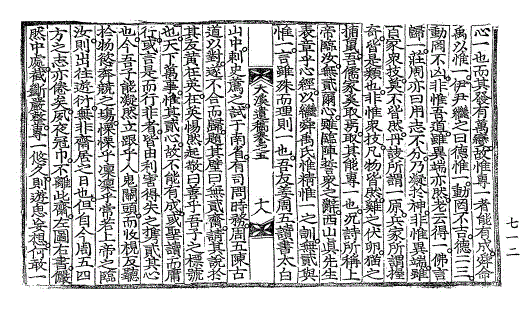 心一也而其发有万变。故惟专一者能有成。舜命禹以惟一。伊尹继之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非惟吾道。虽异端亦然。老云得一。佛言归一。庄周亦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非惟异端。虽百家众技。莫不皆然。丹诀所谓一原。兵家所谓握奇。皆是类也。非惟众技。凡物皆然。鸡之伏卵。猫之捕鼠。吾儒家奚取焉。取其能专一也。况诗所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虽临阵誓众之辞。西山真先生表章乎心经。以继舜禹氏惟精惟一之训。无贰与惟一。言虽殊而理则一也。吾友姜周五读书太白山中。刺史荐之。试于南省。有司问时务。周五陈古道以对。遂不合而归。题其壁曰无贰斋。请其说于其友黄在英。在英惕然起敬曰善乎吾子之标号也。天下万事。惟其贰心。故不能有成。或圣读而庸行。或言是而行非者。皆由利害得失之携贰其心也。今吾子能凝然立跟乎人鬼关头。而收视反听于物欲奔竞之场。慄慄乎凛凛乎常若上帝之临汝。则出往游衍。无非斋居之日也。但自今周五四方之志亦倦矣。夙夜冠巾。不离此斋。左图右书。俨然中处。截断严整。专一悠久。则游思妄想。何敢一
心一也而其发有万变。故惟专一者能有成。舜命禹以惟一。伊尹继之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非惟吾道。虽异端亦然。老云得一。佛言归一。庄周亦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非惟异端。虽百家众技。莫不皆然。丹诀所谓一原。兵家所谓握奇。皆是类也。非惟众技。凡物皆然。鸡之伏卵。猫之捕鼠。吾儒家奚取焉。取其能专一也。况诗所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虽临阵誓众之辞。西山真先生表章乎心经。以继舜禹氏惟精惟一之训。无贰与惟一。言虽殊而理则一也。吾友姜周五读书太白山中。刺史荐之。试于南省。有司问时务。周五陈古道以对。遂不合而归。题其壁曰无贰斋。请其说于其友黄在英。在英惕然起敬曰善乎吾子之标号也。天下万事。惟其贰心。故不能有成。或圣读而庸行。或言是而行非者。皆由利害得失之携贰其心也。今吾子能凝然立跟乎人鬼关头。而收视反听于物欲奔竞之场。慄慄乎凛凛乎常若上帝之临汝。则出往游衍。无非斋居之日也。但自今周五四方之志亦倦矣。夙夜冠巾。不离此斋。左图右书。俨然中处。截断严整。专一悠久。则游思妄想。何敢一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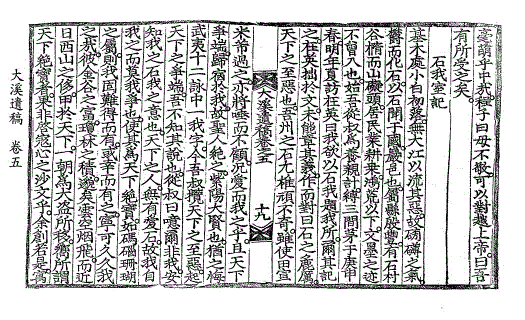 毫萌乎中哉。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曰吾有所受之矣。
毫萌乎中哉。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曰吾有所受之矣。石我室记
基木处小白初落。无大江以流其恶。故磅礴之气。郁而化石。以石闻于国。岩邑也。属县殷丰。有石村谷椭而山碍头。居民业耕桑。鸿荒以下。文墨之迹不曾入也。始吾从叔为养亲计。缚三间茅于庚申春。明年夏访在英曰我欲以石我题我所。尔其记之。在英拙于文。未能章其义。作而对曰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吾州之石尤椎顽不奇。虽使田宣米芾过之。亦将唾而不顾。况爱而我之乎。且天下争端。归宿于我。故圣人绝之。紫阳大贤也。犹之悔武夷十二咏中一我字。今吾叔揽天下之至恶。起天下之争端。吾不知其说也。从叔曰噫尔非我。安知我之石我之意也。天下之人。无有爱石。故我自我之而莫我争也。使其为天下绝宝。如码碯珊瑚之属。则我固难得而有。或幸而有之。宁可久久我之哉。彼金谷之富。琼林之积。邈矣云空烟飞。而近日西山之侈。甲于天下。一朝为大盗所移。向所谓天下绝宝者。果非启寇心之沙文乎。余创若是。寓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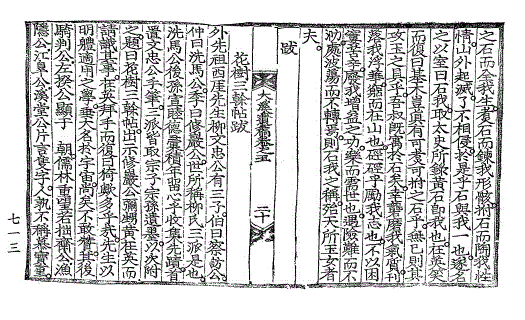 之石而全我生。煮石而鍊我形骸。拊石而陶我性情。山外起灭。了不相侵。于是乎石与我一也。遂名之以室曰石我。取太史所录黄石即我也。在英笑而复曰基木岂真有可煮可拊之石乎。无已则其攻玉之具乎。吾叔既寓于石矣。幸砻磨我气质。刊落我浮华。穷而在山也。硁硁乎励我志也。不以困窭苦辛。废我增益之功。乐而需世也。遇险难而不泐。处波荡而不转焉。则石我之称。殆天所玉女者夫。
之石而全我生。煮石而鍊我形骸。拊石而陶我性情。山外起灭。了不相侵。于是乎石与我一也。遂名之以室曰石我。取太史所录黄石即我也。在英笑而复曰基木岂真有可煮可拊之石乎。无已则其攻玉之具乎。吾叔既寓于石矣。幸砻磨我气质。刊落我浮华。穷而在山也。硁硁乎励我志也。不以困窭苦辛。废我增益之功。乐而需世也。遇险难而不泐。处波荡而不转焉。则石我之称。殆天所玉女者夫。大溪遗稿卷之五
跋
花树三干帖跋
外先祖西厓先生柳文忠公有三子。伯曰察访公。仲曰洗马公。季曰修岩公。世所称柳氏三派是也。洗马公后孙宣睦德汇积年留心乎收集先迹。首置文忠公手笔。三派皆取宗子宗孙遗墨。以次附之。题曰花树三干帖。出示修岩公弥甥黄在英而请识其事。在英拜手而复曰猗欤多乎哉。先生以明体适用之学。垂大名于宇宙。尚矣不敢赞。其后骑判公,左揆公显于 朝。儒林重望若拙斋公,渔隐公,江皋公,溪堂公片言只字。人孰不称慕宝重。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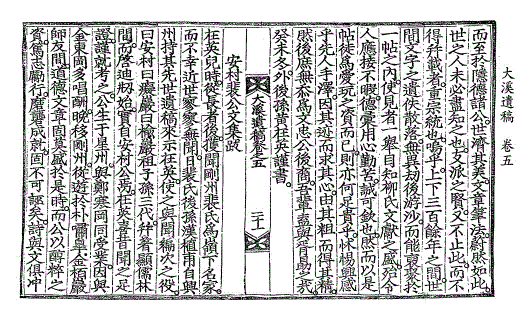 而至于隐德诸公。世济其美。文章笔法。蔚然如此。世之人未必尽知之也。支派之贤。又不止此。而不得并载者。重宗统也。呜乎。上下三百馀年之间。世间文字之遗佚散落。无异劫后游沙。而能裒聚于一帖之内。使见者一举目知柳氏文献之盛。殆令人应接不暇。德汇用心勤苦。诚可钦也。然而以是帖徒为爱玩之资而已。则亦何足贵乎。怵惕兴感乎先人手泽。因其迹而求其心。由其粗而得其精。然后庶无忝为文忠公后裔。吾辈盍与胥勖之哉。癸未冬。外后孙黄在英谨书。
而至于隐德诸公。世济其美。文章笔法。蔚然如此。世之人未必尽知之也。支派之贤。又不止此。而不得并载者。重宗统也。呜乎。上下三百馀年之间。世间文字之遗佚散落。无异劫后游沙。而能裒聚于一帖之内。使见者一举目知柳氏文献之盛。殆令人应接不暇。德汇用心勤苦。诚可钦也。然而以是帖徒为爱玩之资而已。则亦何足贵乎。怵惕兴感乎先人手泽。因其迹而求其心。由其粗而得其精。然后庶无忝为文忠公后裔。吾辈盍与胥勖之哉。癸未冬。外后孙黄在英谨书。安村裴公文集跋
在英儿时。从长者后。获闻刚州裴氏为岭下名家。而不幸近世寥寥无闻。日裴氏后孙汉植甫自兴州持其先世遗稿来示在英。使之与闻编次之役。曰安村曰痴岩曰榆岩祖子孙三代。并著显儒林间。而启迪刱始。实自安村公焉。在英喜昔闻之足證。谨就考之。公生于星州。与郑寒冈同受业。因与金东冈多唱酬。晚移刚州。从游于朴啸皋,金柏岩师友间。道德文章固莫盛于是时。而公以醇粹之资。笃志励行。磨砻成就。固不可诬矣。诗与文俱冲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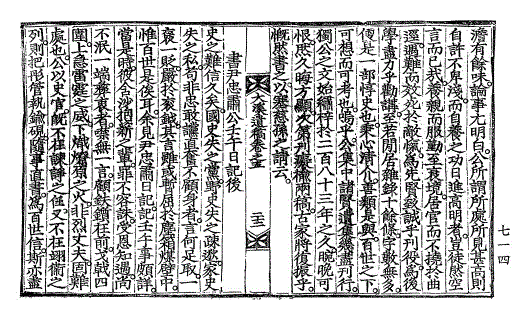 澹有馀味。论事尤明白。公所谓所处所见甚高则自许不卑浅。而自养之功日进高明者。岂徒然空言而已哉。养亲而服勤至衰境。居官而不挠于曲径。遇难而效死于敌忾。为先贤致诚乎刊役。为后学尽力乎劝讲。至若閒居杂录十馀条。字数无多。便是一部惇史也。秉心清介。善类是与。百世之下。可想而可考也。呜乎。公集中诸贤遗集几尽刊行。独公之文始绣梓于二百八十三年之久。晼晚可恨。然久晦方显。次第刊痴榆两稿。古家将复振乎。慨然书之。以塞慈孙之请云。
澹有馀味。论事尤明白。公所谓所处所见甚高则自许不卑浅。而自养之功日进高明者。岂徒然空言而已哉。养亲而服勤至衰境。居官而不挠于曲径。遇难而效死于敌忾。为先贤致诚乎刊役。为后学尽力乎劝讲。至若閒居杂录十馀条。字数无多。便是一部惇史也。秉心清介。善类是与。百世之下。可想而可考也。呜乎。公集中诸贤遗集几尽刊行。独公之文始绣梓于二百八十三年之久。晼晚可恨。然久晦方显。次第刊痴榆两稿。古家将复振乎。慨然书之。以塞慈孙之请云。书尹忠肃公壬午日记后
史之难信久矣。国史失之党。野史失之疏逖。家史失之私。苟非忠敢谠直奋不顾身者。言何足取。一褒一贬。严于衮钺。其言虽或暂屈于尘箱煤壁中。惟百世是俟耳。余见尹忠肃日记。记壬午事颇详。当是时。彼含沙抱薪之辈。罪不容诛。受恩知遇。尚不泯一端彝衷者。噤无一言。顾鈇锧在前。戈戟四围。上急雷霆之威。下炽燎原之火。非烈丈夫。固难处也。公以史官。既不在谏诤之任。又不在翊卫之列。则把彤管执鍮砚。随事直书。为百世信。斯亦尽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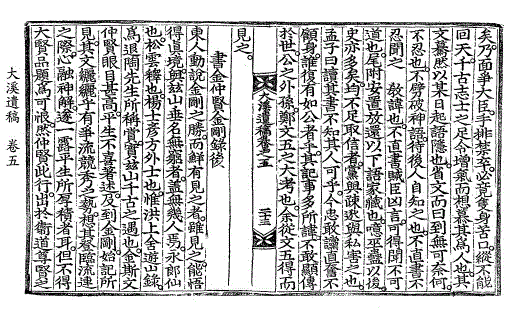 矣。乃面争大臣。手排禁卒。必竟只身苦口。纵不能回天。千古志士之足令增气而想慕其为人也。其文蓦然以某日起语隐也。省文而曰到无可奈何。不忍也。不劈破神语。待后人自知之也。不直书不忍闻之 教讳也。不直书贼臣凶言。可得闻不可道也。尾附安置放还以下语家藏也。噫巫蛊以后。史亦多矣。均不足取信者。党与疏逖与私害之也。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今忠敢谠直奋不顾身。谁复有如公者乎。其记事多所讳。不敢显传于世。公之外孙。郑文五之大考也。余从文五得而见之。
矣。乃面争大臣。手排禁卒。必竟只身苦口。纵不能回天。千古志士之足令增气而想慕其为人也。其文蓦然以某日起语隐也。省文而曰到无可奈何。不忍也。不劈破神语。待后人自知之也。不直书不忍闻之 教讳也。不直书贼臣凶言。可得闻不可道也。尾附安置放还以下语家藏也。噫巫蛊以后。史亦多矣。均不足取信者。党与疏逖与私害之也。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今忠敢谠直奋不顾身。谁复有如公者乎。其记事多所讳。不敢显传于世。公之外孙。郑文五之大考也。余从文五得而见之。书金仲贤金刚录后
东人动说金刚之胜。而鲜有见之者。虽见之。能悟得真境。与玆山垂名无穷者。盖无几人焉。永郎仙也。松云释也。杨士彦方外士也。惟洪上舍游山录。为退陶先生所称赏。实玆山千古之遇也。金斯文仲贤眼目甚高。平生不喜著述。及到金刚。始记所见。其文纚纚乎有争流竞秀之势。想其登临流连之际。心融神解。遂一露平生所厚积者耳。但不得大贤品题为可恨。然仲贤此行。出于卫道尊贤之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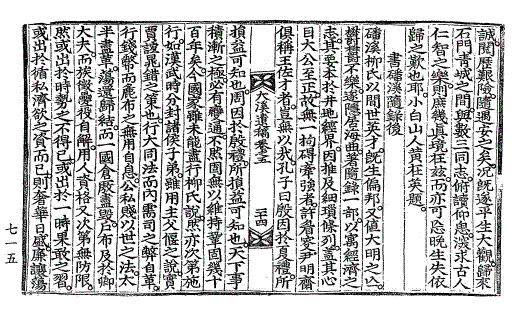 诚。阅历艰险。随遇安之矣。况既遂平生大观。归来石门青城之间。与数三同志。俯读仰思。深求古人仁智之乐。则庶几真境在玆。而亦可忘晚生失依归之叹也耶。小白山人黄在英题。
诚。阅历艰险。随遇安之矣。况既遂平生大观。归来石门青城之间。与数三同志。俯读仰思。深求古人仁智之乐。则庶几真境在玆。而亦可忘晚生失依归之叹也耶。小白山人黄在英题。书磻溪随录后
磻溪柳氏以间世英才。既生偏邦。又值大明之亡。郁郁不乐。遂隐居海曲。著随录一部。以寓经济之志。其要本于井地经界。因推及细琐条列。盖其心目大公至正。故无一拘碍牵强者。许眉叟,尹明斋俱称王佐才者。岂无以哉。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天下事积渐之极。必有变通。不然固无以维持巩固几十百年矣。今国家虽未能尽行柳氏说。然亦次第施行。如汉武时分封诸侯子弟。虽用主父偃之说。实贾谊晁错之策也。行大同法而内需司之弊自革。行钱币而粗布之无用自息。公私贱以世之法。太半尽革。荡还归结。而一国仓廒尽毁。户布及于卿大夫。而族徵叠役自解。用人资格又次第无防限。然或出于时势之不得已。或出于一时果敢之习。或出于循私济欲之资而已。则奢华日盛。廉让荡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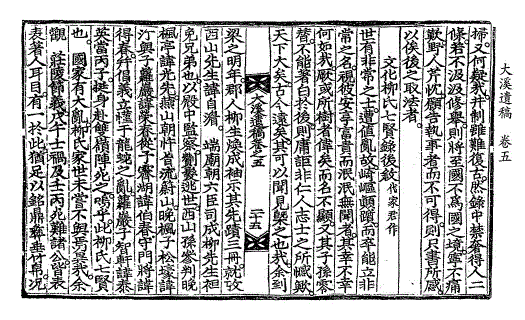 扫。又何疑哉。井制虽难复古。然录中禁奢得人二条。若不汲汲修举。则将至国不为国之境。宁不痛叹。野人芹忱。愿告执事者而不可得。则只书所感。以俟后之取法者。
扫。又何疑哉。井制虽难复古。然录中禁奢得人二条。若不汲汲修举。则将至国不为国之境。宁不痛叹。野人芹忱。愿告执事者而不可得。则只书所感。以俟后之取法者。文化柳氏七贤录后叙(代家君作)
世有非常之士。遭值乱故。崎岖颠踬。而卒能立非常之名。视彼安享富贵而泯泯无闻者。其幸不幸何如哉。厥或所树者伟矣而名不显。又其子孙零替。不能著白于后。则庸讵非仁人志士之所憾欤。天下大矣。古今远矣。其可以闻见槩之也哉。余到梁之明年。郡人柳生焕成袖示其先迹三册。就考西山先生讳自湄。 端庙朝六臣司成柳先生袒免兄弟也。以殿中监察。剪发逃世。西山孙参判晚枫亭讳光先。燕山朝忤旨流蔚山。晚枫子松壕讳汀与子萝岩讳荣春,从子霁湖讳伯春,守门将讳得春。并倡义立慬于龙蛇之乱。萝岩子智轩讳泰英当丙子。挺身赴双岭阵死之。呜乎。此柳氏七贤也。 国家有大乱。柳氏家世未尝不与焉异哉。余观 庄陵节义。戊午士祸及壬丙死难诸公。皆表表著人耳目。有一于此。犹足以铭鼎彝垂竹帛。况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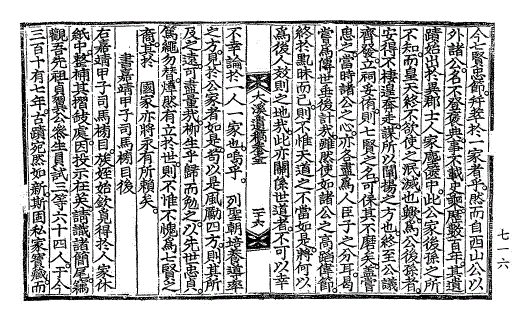 今七贤忠节。并萃于一家者乎。然而自西山公以外诸公。名不登褒典。事不载史乘。历数百年。其遗迹始出于异郡士人家尘箧中。此公家后孙之所不知。而皇天终不欲使之泯灭也欤。为公后孙者。安得不栖遑奔走。谋所以阐扬之方也。终至公议齐发。立祠妥侑。则七贤之名。可保其不磨矣。盖尝思之。当时诸公之心。亦各尽为人臣子之分耳。曷尝为传世垂后计哉。虽然使如诸公之高蹈伟节。终于䵝昧而已。则不惟天道之不当如是。将何以为后人效则之地哉。此亦关系世道者。不可以幸不幸论于一人一家也。呜乎。 列圣朝培养导率之方。见于公家者如是。苟以是风励四方。则其所及之远。可尽量哉。柳生乎归而勉之。以先世忠贞。笃绳勿替。㷆然有立于世。则不惟不愧为七贤之裔。其于 国家亦将永有所赖矣。
今七贤忠节。并萃于一家者乎。然而自西山公以外诸公。名不登褒典。事不载史乘。历数百年。其遗迹始出于异郡士人家尘箧中。此公家后孙之所不知。而皇天终不欲使之泯灭也欤。为公后孙者。安得不栖遑奔走。谋所以阐扬之方也。终至公议齐发。立祠妥侑。则七贤之名。可保其不磨矣。盖尝思之。当时诸公之心。亦各尽为人臣子之分耳。曷尝为传世垂后计哉。虽然使如诸公之高蹈伟节。终于䵝昧而已。则不惟天道之不当如是。将何以为后人效则之地哉。此亦关系世道者。不可以幸不幸论于一人一家也。呜乎。 列圣朝培养导率之方。见于公家者如是。苟以是风励四方。则其所及之远。可尽量哉。柳生乎归而勉之。以先世忠贞。笃绳勿替。㷆然有立于世。则不惟不愧为七贤之裔。其于 国家亦将永有所赖矣。书嘉靖甲子司马榜目后
右嘉靖甲子司马榜目。族侄始钦觅得于人家休纸中。整补其摺缺处。因投示在英。请识诸简尾。窃观吾先祖贞翼公参生员试三等六十四人。于今三百十有七年。古迹宛然如新。斯固私家宝藏。而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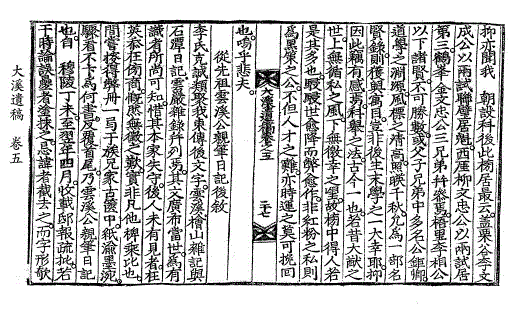 抑亦闻我 朝设科后此榜居最云。盖栗谷李文成公以两试联璧居魁。西厓柳文忠公以两试居第三。鹤峰金文忠公三兄弟并参焉。梧里李相公以下诸贤。不可胜数。或父子兄弟中多名公钜卿。道学之渊源。风标之清高。照映千秋。允为一部名贤录。则获与寓目。岂非后生末学之一大幸耶。抑因此窃有感焉。科举之法。古今一也。若昔大猷之世。上无循私之风。下无徼幸之望。故榜中得人若是其多也。骎骎世愈降而弊愈作。非红粉之私则为黑策之公。不但人才之难。亦时运之莫可挽回也。呜乎悲夫。
抑亦闻我 朝设科后此榜居最云。盖栗谷李文成公以两试联璧居魁。西厓柳文忠公以两试居第三。鹤峰金文忠公三兄弟并参焉。梧里李相公以下诸贤。不可胜数。或父子兄弟中多名公钜卿。道学之渊源。风标之清高。照映千秋。允为一部名贤录。则获与寓目。岂非后生末学之一大幸耶。抑因此窃有感焉。科举之法。古今一也。若昔大猷之世。上无循私之风。下无徼幸之望。故榜中得人若是其多也。骎骎世愈降而弊愈作。非红粉之私则为黑策之公。不但人才之难。亦时运之莫可挽回也。呜乎悲夫。从先祖云溪公亲笔日记后叙
李氏克诚类聚我东传后文字。云溪,桧山杂记与石潭日记,云岩杂录并列焉。其文广布当世。为有识者所尚可知。惜其本家失守。后人未有见者。在英忝在傍裔。慨然无徵之叹。实非凡他稗乘比也。间尝搜得弊册一𢎥于族兄家古箧中。纸渝墨涴。骤看不卞为何书。反覆首尾。乃云溪公亲笔日记也。自 穆陵丁未。至翌年四月。收载邸报疏批。若干时论误叠者涂抹之。忌讳者截去之。而字形欹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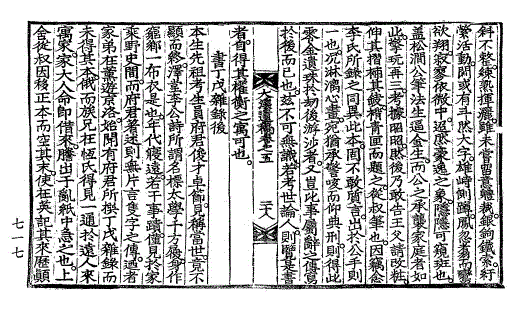 斜不整。练熟挥洒。虽未尝留意体裁。银钩铁索。纡萦活动。间或有斗然大字。雄峙侧蹲。凤忽翥而鸾欲翔。寂寥依微中。迢然豪逸之象。隐隐可窥斑也。盖松涧公笔法生逼金生。而公之承袭家庭者如此。擎玩再三。考据昭昭。然后乃敢告王父请改妆。伸其摺补其缺。褙青匣而题之。从叔笔也。因窃念李氏所录之同异此本。固不敢质言。出于公手则一也。况淋漓心画。宛犹承警咳而仰典刑。则得此零金遗珠于劫后游沙者。又岂比事属辞之传写于后而已也。玆不可无识。若考世论人。则览是书者。自得其权衡之寓可也。
斜不整。练熟挥洒。虽未尝留意体裁。银钩铁索。纡萦活动。间或有斗然大字。雄峙侧蹲。凤忽翥而鸾欲翔。寂寥依微中。迢然豪逸之象。隐隐可窥斑也。盖松涧公笔法生逼金生。而公之承袭家庭者如此。擎玩再三。考据昭昭。然后乃敢告王父请改妆。伸其摺补其缺。褙青匣而题之。从叔笔也。因窃念李氏所录之同异此本。固不敢质言。出于公手则一也。况淋漓心画。宛犹承警咳而仰典刑。则得此零金遗珠于劫后游沙者。又岂比事属辞之传写于后而已也。玆不可无识。若考世论人。则览是书者。自得其权衡之寓可也。书丁戊杂录后
本生先祖考生员府君俊才卓节。见称当世。竟不显而终。泽堂李公诗所谓名标太学千方履。身作穷乡一布衣是也。年代寝远。若干事迹。仅见于家乘野史间。而府君著述则无片言只字之传。乃者家弟在薰游京洛。始闻有府君所撰丁戊杂录而未得其本。俄而族兄在恒氏得见一通于远人来寓家。家大人命即借来。誊出于乱纸中急之也。上舍从叔因移正本而空其末。使在英记其来历颠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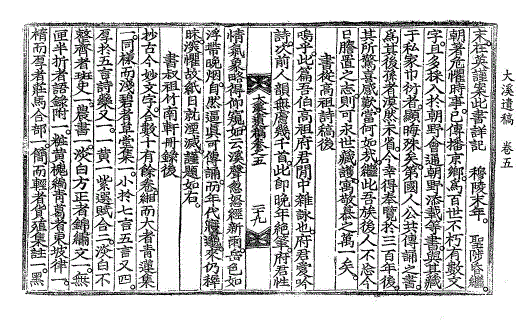 末。在英谨案此书详记 穆陵末年。 圣陟昏继。朝著危惧时事。已传播京乡。为百世不朽有数文字。且多采入于朝野会通朝野添载等书。与其藏于私家巾衍者。显晦殊矣。第国人公共传诵之书。为其后孙者漠然未省。今幸得奉览于三百年后。其所惊喜感叹。当何如哉。继此吾族后人不忘今日誊置之志。则可永世藏护。寓敬慕之万一矣。
末。在英谨案此书详记 穆陵末年。 圣陟昏继。朝著危惧时事。已传播京乡。为百世不朽有数文字。且多采入于朝野会通朝野添载等书。与其藏于私家巾衍者。显晦殊矣。第国人公共传诵之书。为其后孙者漠然未省。今幸得奉览于三百年后。其所惊喜感叹。当何如哉。继此吾族后人不忘今日誊置之志。则可永世藏护。寓敬慕之万一矣。书从高祖诗稿后
呜乎。此篇吾伯高祖府君閒中杂咏也。府君爱吟诗。次前人韵无虑几千首。此即晚年绝笔。府君性情气象略得仰窥。如云溪声忽怒经新雨。岳色如浮带晚烟。自然逼真可传诵。而年代寝邈。来仍稚昧。深惧故纸日就湮灭。谨题如右。
书叔祖竹南轩册录后
抄古今妙文字。合数十有馀卷。缃而大者青莲集一。同样而浅碧者草堂集一。小于七言五言又四。厚于五言诗药又一。一黄一紫选赋合二。淡白不整齐者斑史一。农书一。淡白方正者锦绣文一。无匣半折者语录附一。妆黄槐编青葛者东坡律一。椭而厚者庄马合部一。简而轻者货殖集注一。黑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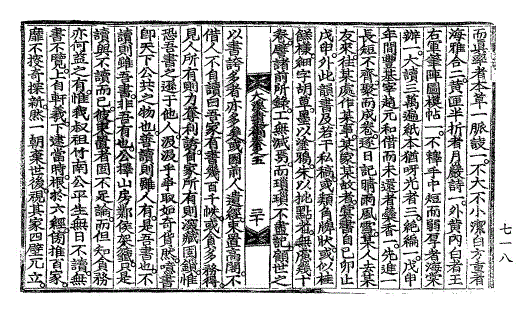 而真率者本草一脉诀一。不大不小洁白方重者海雅合二。黄匣半折者月岩诗一。外黄内白者王右军笔阵图模帖一。不释手中短而弱厚者海棠办一。大读三万遍纸本犹呀光者三。绝编一。戊申年间丰基宰赵元和借而未还者蕊香一。先进一长短不齐。聚而成卷。逐日记晴雨风雪。某人去某友来。往某处作某事。某家某故者。蓂书自己卯止戊申。外此韵书及若干私稿。或类角牌状。或似桂糕样。细字胡草。墨以涂鸦。朱以批点者。无虑几十卷。譬诸前所录。工无减焉。而琐琐不尽记。顾世之以书誇多者亦多矣。或因前人遗经。束置高阁。不借人不自读曰吾家有书几百千帙。或贪多务得。见人所有则力夺利诱。自家所有则深藏固锁。惟恐吾书之逊于他人。汲汲乎争取如奇货然。噫书即天下公共之物也。善读则虽人有。是吾书也。不读则虽吾书。非吾有也。公择山房邺侯架签。只是读与不读而已。彼束置者固不足论。而但知贪务亦何益之有。惟我叔祖竹南公平生无日不读。无书不览。上自轩羲。下逮当时。根于六经。傍推百家。靡不搜奇探新。然一朝弃世后。视其家四壁兀立。
而真率者本草一脉诀一。不大不小洁白方重者海雅合二。黄匣半折者月岩诗一。外黄内白者王右军笔阵图模帖一。不释手中短而弱厚者海棠办一。大读三万遍纸本犹呀光者三。绝编一。戊申年间丰基宰赵元和借而未还者蕊香一。先进一长短不齐。聚而成卷。逐日记晴雨风雪。某人去某友来。往某处作某事。某家某故者。蓂书自己卯止戊申。外此韵书及若干私稿。或类角牌状。或似桂糕样。细字胡草。墨以涂鸦。朱以批点者。无虑几十卷。譬诸前所录。工无减焉。而琐琐不尽记。顾世之以书誇多者亦多矣。或因前人遗经。束置高阁。不借人不自读曰吾家有书几百千帙。或贪多务得。见人所有则力夺利诱。自家所有则深藏固锁。惟恐吾书之逊于他人。汲汲乎争取如奇货然。噫书即天下公共之物也。善读则虽人有。是吾书也。不读则虽吾书。非吾有也。公择山房邺侯架签。只是读与不读而已。彼束置者固不足论。而但知贪务亦何益之有。惟我叔祖竹南公平生无日不读。无书不览。上自轩羲。下逮当时。根于六经。傍推百家。靡不搜奇探新。然一朝弃世后。视其家四壁兀立。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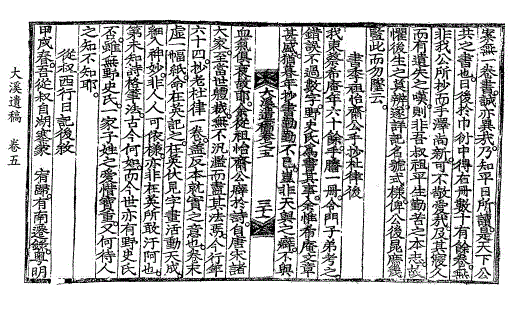 案无一卷书。诚亦异哉。乃知平日所读。是天下公共之书也。日后于巾衍中得右册数十有馀卷。无非我公所抄而手泽尚新。可不敬爱哉。及其寝久而有遗失之叹。则非吾叔祖平生勤苦之本志。故惧后生之莫辨。遂详记名号式样。俾公后昆庶几监此而勿坠云。
案无一卷书。诚亦异哉。乃知平日所读。是天下公共之书也。日后于巾衍中得右册数十有馀卷。无非我公所抄而手泽尚新。可不敬爱哉。及其寝久而有遗失之叹。则非吾叔祖平生勤苦之本志。故惧后生之莫辨。遂详记名号式样。俾公后昆庶几监此而勿坠云。书季祖怡斋公手抄杜律后
我东蔡希庵年六十馀。手誊一册。令门子弟考之。错误不过数字。野史氏为书其事。余惟希庵文章甚盛。犹暮年抄书勤勤不已。岂非天与之癖。不与血气俱衰故耶。余从祖怡斋公癖于诗。自唐宋诸大家。至当世体裁。无不汎滥而尽其法焉。今行年六十四。抄老杜律一卷。盖反本就实之意也。卷末虚一幅纸。命在英记之。在英伏见字画活动天成。细入神妙。非人人可依样。亦非在英所敢污阿也。第未知诗格笔法。古今何如。而今世亦有野史氏否。虽无野史氏。一家子姓之爱惜宝重。又何待人之知不知耶。
从叔西行日记后叙
甲戌春。吾从叔自湖塞蒙 宥归。有南迁录。粤明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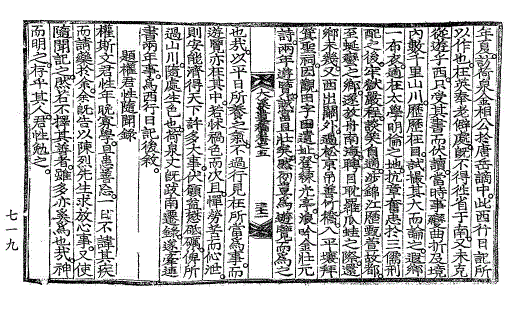 年夏。访荷泉金相公于唐岳谪中。此西行日记所以作也。在英奉老僻处。既不得往省于南。又未克从游乎西。只受其书而伏读。当时事变曲折及境内数千里山川。历历在目。试撮其大而论之。遐乡一布衣。适在太学明伦之地。抗章奋忠于三儒刑配之后。牢狱严程。谈笑自适。涉锦江历甄萱故都。至蜒蛮之乡。遂放舟南海。聘目耽罗爪蛙之际。还乡未几。又西出关外。过松京吊善竹桥。入平壤拜箕圣祠。因观田字田遗址。登练光亭。浪吟金壮元诗。两年游览。诚富且壮矣。然初岂为游览而为之也哉。以平日所养之气。不过行见在所当为事。而游览亦在其中。若怵祸色而次且。惮劳苦而伈泄。则安能济得天下许多大事。伏愿益懋砥砺。俾所过山川。随处生色也。荷泉丈既跋南迁录。遂牵连书两年事。为西行日记后叙。
年夏。访荷泉金相公于唐岳谪中。此西行日记所以作也。在英奉老僻处。既不得往省于南。又未克从游乎西。只受其书而伏读。当时事变曲折及境内数千里山川。历历在目。试撮其大而论之。遐乡一布衣。适在太学明伦之地。抗章奋忠于三儒刑配之后。牢狱严程。谈笑自适。涉锦江历甄萱故都。至蜒蛮之乡。遂放舟南海。聘目耽罗爪蛙之际。还乡未几。又西出关外。过松京吊善竹桥。入平壤拜箕圣祠。因观田字田遗址。登练光亭。浪吟金壮元诗。两年游览。诚富且壮矣。然初岂为游览而为之也哉。以平日所养之气。不过行见在所当为事。而游览亦在其中。若怵祸色而次且。惮劳苦而伈泄。则安能济得天下许多大事。伏愿益懋砥砺。俾所过山川。随处生色也。荷泉丈既跋南迁录。遂牵连书两年事。为西行日记后叙。题权君性随闻录
权斯文君性年晚寡学。且患善忘。一日不讳其疾而请药于余。余既告以陈烈先生求放心事。又使随闻记之。然若不择其善者。虽多亦奚为也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君性勉之。
大溪遗稿卷之五
杂著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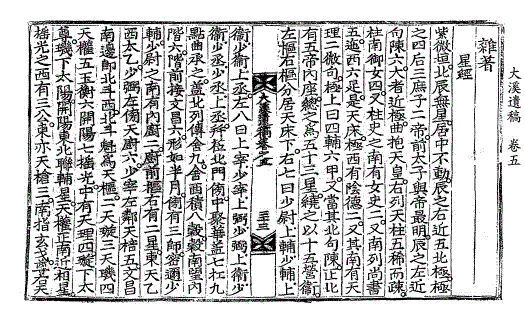 星经
星经紫微垣。北辰无星。居中不动。辰之右近五北极。极之四后三庶子二帝。前太子与帝最明。辰之左近句陈六。大者近极。曲抱天皇。右列天柱五稀而疏。柱南御女四。又柱史之南有女史二。又南列尚书五。迤西六足。是天床。极西有阴德二。又其南有天理二微句。极上曰四辅六甲。又当其北句陈。正北有五帝内座。总之为五十三星。绕之以十五营卫。左枢右枢分居天床下。右七曰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左八曰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卫,少卫,少丞,少丞,上丞。并莅北门傍。中聚华盖七扛九点曲承之。盖北列传舍九。舍西积八谷。谷南望内阶六。阶前接文昌六。形如半月。傍有三师。密迩少辅。少尉之南有内厨二。厨前枢右有二星。东天乙西太乙。少弼左傍天厨六。少宰左邻天棓五。文昌南边即北斗西。北斗魁为天枢。天天璇三天玑四天权五玉衡六开阳七摇光。中有天理四。璇下太尊。玑下太阳。开阳东北联辅星。天权正南近相星。摇光之西有三公。东亦天枪三。南指玄戈。尊右天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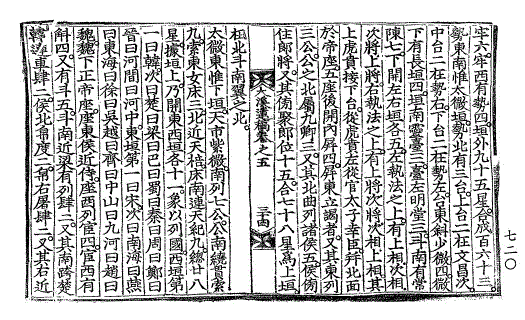 牢六。牢西有势四。垣外九十五星。合成百六十三。
牢六。牢西有势四。垣外九十五星。合成百六十三。势东南惟太微垣。势北有三台。上台二在文昌次。中台二在势右。下台二在势左。台东斜少微四。微下有长垣四。垣南灵台三。台左明堂三。斗南有常陈七。下开左右垣各五。左执法之上。有上相,次相,次将,上将。右执法之上。有上将,次将,次相,上相。其上虎贲接下台。从虎贲左从官太子幸臣。并北面于帝座。五座后开内屏四。屏东立谒者。又其东列三公。公之北属九卿三。又其北曲列诸侯五。侯傍住郎将。又其傍聚郎位十五。合七十八星为上垣。在北斗南翼之北。
太微东惟下垣。天市紫微。南列七公。公南绕贯索九。索东女床三。北近天棓。床南连天纪九。总廿八星。据垣上。乃开东西垣各十一。象以列国。西垣第一曰韩。次曰楚曰梁曰巴曰蜀曰秦曰周曰郑曰晋曰河间曰河中。东垣第一曰宋。次曰南海曰燕曰东海曰徐曰吴越曰齐曰中山曰九河曰赵曰魏。魏下正帝座。座东侯近侍。座西列宦四。宦西有斛四。又有斗五。斗南近梁有列肆二。又其南跨楚韩连车肆二。侯北帛度二。帛右屠肆二。又其右近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1H 页
 齐有宗二。迤而南有宗人四。又其左有宗正二。南布市楼六。右依南海。左连车肆。已上合八十七星。
齐有宗二。迤而南有宗人四。又其左有宗正二。南布市楼六。右依南海。左连车肆。已上合八十七星。太微左惟角二。履天门二。戴天田二。又其上浮周鼎三。实诸侯北。角左右横平道二。道西又着进贤。更从天门下斜平二。平下起库楼十衡四。微句于中柱十一。乱投内外垂地耀南门二。总四十一星。据十二度。去极九十一度。
角东亢四。北詹大角于左右摄提各三之间。南横折威七。威下西则阳门二。东则顿顽二。总二十二星。据九度。去极八十九度。
亢东氐四。东顾天乳。乳北西望亢池四。池西北仰帝座三。二在亢分。一角墟座。东斜梗河三。河上浮招摇。直冲斗柄末。氐下有天辐二。辐西横津车三。其南聚骑官十。又有骑阵将军及车骑三。总三十五星。据十五度。去极九十七度。
氐东房四。左附钩铃二。下列从官二。右窥西咸四。悬其下者曰日。左窥东咸四。居其间者即键闭。上有罚三。当梁楚之际。总二十一星。据五度。去极百八度。
房东心三。下有积卒二。总五星。上仝。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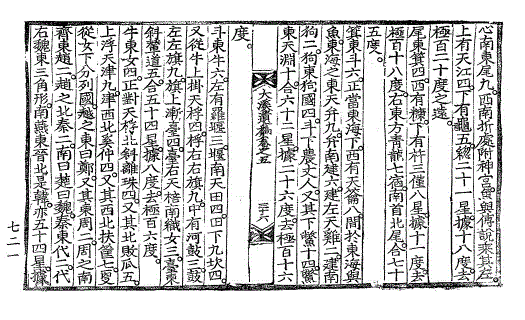 心南东尾九。西南折处附神宫。鱼与傅说乘其左。上有天江四。下有龟五。总二十一星。据十八度。去极百二十度之远。
心南东尾九。西南折处附神宫。鱼与傅说乘其左。上有天江四。下有龟五。总二十一星。据十八度。去极百二十度之远。尾东箕四。西有糠。下有杵三仅八星。据十一度。去极百十八度。右东方青龙七宿。南首北尾。合七十五度。
箕东斗六。正当东海下。西有天籥八。间于东海与鱼。东海之东天弁九。弁南建六。建左天鸡二。建南狗二。狗东狗国四。斗下农丈人。又其下鳖十四。鳖东天渊十。合六十二星。据二十六度。去极百十六度。
斗东牛六。左有罗堰三。堰南天田四。田下九坎四。又从牛上挂天桴四。桴右右旗九。中有河鼓三。鼓左左旗九。旗上渐台四。台右天棓南织女三。台东斜辇道五。合五十四星。据八度。去极百六度。
牛东女四。正对天桴北斜离珠四。又其北败瓜五。上浮天津九。津西北奚仲四。又其西北扶筐七。更从女下分列国。越之东曰郑。又其东周二。周之南齐东赵二。赵之北秦二。南曰楚曰魏。秦东代二。代右魏东三角形。南燕东晋北是韩。亦五十四星。据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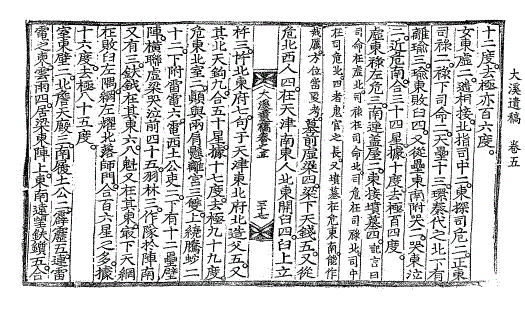 十二度。去极亦百六度。
十二度。去极亦百六度。女东虚二。遥相接。北指司中二。东探司危二。正东司禄二。禄下司命二。天垒十三。环秦代之北下有离瑜三。瑜东败臼四。又从垒东南附哭二。哭东泣二。近危南。合三十四星。据十度。去极百四度。
虚东禄左危三。南连盖屋二。东接坟墓四。(记言曰司命在虚北。司禄在司命北。司危在司禄北。司中在司危北。四者鬼官之长。又坟墓在危东南。能作灾厉。方位当更考。)墓前虚梁四。梁下天钱五。又从危北西人四。在天津南东人北东开臼四。臼上立杵三。杵北东府七。句于天津东北府北造父五。又其北天钩九。合五十星。据十七度。去极九十九度。
危东北室二。颠与两肩悬离宫三双。上绕腾蛇二十二。下附雷电六。电西土公吏二。下有十二垒壁阵。横联虚梁哭泣前四十五。羽林三。作队于阵南又有三。鈇钺在其东六。八魁又在其东。最下天网在败臼左隅。网左耀北落师门。合百六星之多。据十六度。去极八十五度。
室东壁二。北詹天厩三。南履土公二。霹雳五。连雷电之东。云雨四。居梁东阵上。东南远望鈇锧五。合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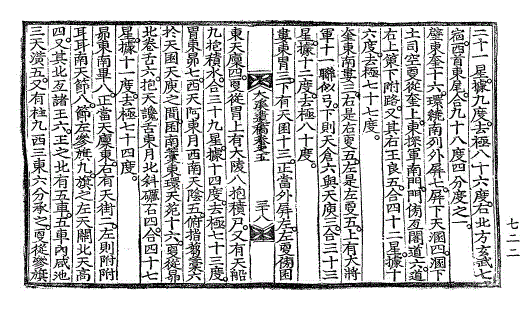 二十一星。据九度。去极八十六度。右北方玄武七宿。西首东尾。合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
二十一星。据九度。去极八十六度。右北方玄武七宿。西首东尾。合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壁东奎十六。环绕南列外屏七。屏下天溷四。溷下土司空更从奎上。东探军南门。门傍亘阁道六。道右上策下附路。又其右王良五。合四十二星。据十六度。去极七十七度。
奎东南娄三。右是右更五。左是左更五。上有大将军十一联似弓。下则天仓六与天庾三。合三十三星。据十二度。去极八十度。
娄东胃三。下有天囷十三。正当外屏左。左更傍囷东天廪四。更从胃上有大陵八抱积尸。又有天船九抱积水。合三十九星。据十四度。去极七十三度。
胃东昴七。西天阿东月西南天阴五。俯指刍稿六于天囷天庾之间。囷南稿东环天苑十六。更从昴北卷舌六。抱天谗舌东月北斜砺石四。合四十七星。据十一度。去极七十四度。
昴东南毕八。正当天廪东。右有天街二。左则附附耳耳南天节八。节左参旗九。旗之左天关北天高四。又其北亘诸王六。王之北有五车。五车内咸池三天潢五。又有柱九西三东六分承之。更从参旗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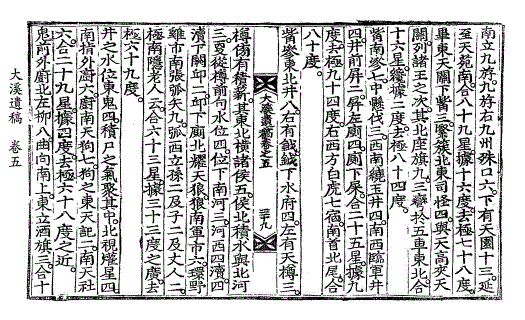 南立九斿。九斿右九州殊口六。下有天园十三。延至天苑南。合八十九星。据十六度。去极七十八度。
南立九斿。九斿右九州殊口六。下有天园十三。延至天苑南。合八十九星。据十六度。去极七十八度。毕东天关下觜三。紧簇北东司怪四。与天高夹天关。列诸王之次。其北座旗九。三弯于五车东北。合十六星。才据二度。去极八十四度。
觜南参七。中悬伐三。西南绕玉井四。南西临军井四。井前屏二。屏左厕四。厕下屎。合二十五星。据九度。去极九十四度。右西方白虎七宿。南首北尾。合八十度。
觜参东北井八。右有钺。钺下水府四。左有天樽三。樽傍有积薪。其东北横诸侯五。侯北积水与北河三。更从樽前句水位四。位下南河三。河西四渎。四渎下阙邱二。邱下厕北耀天狼。狼南军市六。环野鸡市南张弧矢九。弧西立孙二及子二及丈人二。极南隐老人云。合六十三星。据三十三度之广。去极六十九度。
井之水位东鬼四。积尸之气聚其中。北视爟星四。南指外厨六。厨南天狗七。狗之东天记二。南天社六。合二十九星。据四度。去极六十八度之近。
鬼前外厨北左柳八。曲向南上。东立酒旗三。合十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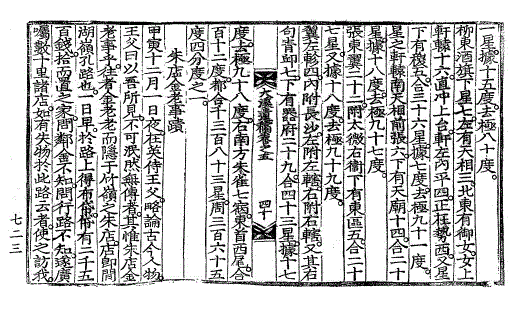 一星。据十五度。去极八十度。
一星。据十五度。去极八十度。柳东酒旗下星七。左有天相三。北东有御女。女上轩辕十六。直冲上台。轩左内平四。正在势西。又星下有稷五。合三十六星。据七度。去极九十一度。
星之轩辕南天相前张六。下有天庙十四。合二十星。据十八度。去极九十七度。
张东翼二十二。附太微右卫下有东区五。合二十七星。又据十八度。去极九十九度。
翼左轸四。内附长沙。左附左辖。右附右辖。又其右句青邱七。下有器府二十九。合四十三星。据十七度。去极九十八度。右南方朱雀七宿。东首西尾。合百十二度。都合千三百八十三星。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朱店金老事迹
甲寅十二月一日夜。在英侍王父。略论古今人物。王父曰以吾所见。不可泯然无传者。其惟朱店金老事乎。往者金老老而隐于竹岭之朱店。店即间湖岭孔路也。一日早。于路上得布袋。袋有二千五百钱。拾而置之家。问邻舍不知。问行路不知。遂广嘱数十里诸店。如有失物于此路云者。使之访我。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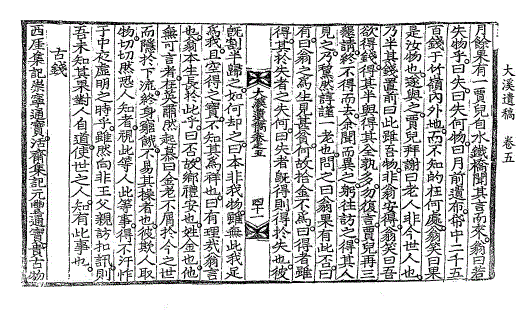 月馀果有一贾儿自水铁桥闻其言而来。翁曰若失物乎。曰失。曰失何物。曰月前遗布。袋中二千五百钱于竹岭内外地。而不知的在何处。翁笑曰果是汝物也。遂与之。贾儿拜谢曰老人非今世人也。乃半其钱置前曰此虽吾物。非翁安得。翁笑曰吾欲得钱。得其半与得其全孰多。勿复言。贾儿再三恳请。终不得而去。余闻而异之。躬往访之。得其人见之。乃黧然谆谨一老也。问之曰翁果有此否。曰有。曰翁之为生见甚贫。何故拾金不为。曰得者虽得。其于失者之失何。曰失者既得则得于失也。彼既割半归之。如何却之。曰本非我物。虽无此我足为我。且空得之宝。不知其为祥也。曰有理哉翁言也。翁本生长于此乎。曰否。故乡礼安也。姓金也。他无可言者。在英肃然起慕曰金老不屑于今之世而隐于下流。终身穷饿。不易其操者也。彼欺人取物。切切然恐人知者。视此等人此等事。得不汗怍于中夜虚明之时乎。虽然向非王父亲访扣讯。则吾未知其果对人自道。使世之人。知有此事也。
月馀果有一贾儿自水铁桥闻其言而来。翁曰若失物乎。曰失。曰失何物。曰月前遗布。袋中二千五百钱于竹岭内外地。而不知的在何处。翁笑曰果是汝物也。遂与之。贾儿拜谢曰老人非今世人也。乃半其钱置前曰此虽吾物。非翁安得。翁笑曰吾欲得钱。得其半与得其全孰多。勿复言。贾儿再三恳请。终不得而去。余闻而异之。躬往访之。得其人见之。乃黧然谆谨一老也。问之曰翁果有此否。曰有。曰翁之为生见甚贫。何故拾金不为。曰得者虽得。其于失者之失何。曰失者既得则得于失也。彼既割半归之。如何却之。曰本非我物。虽无此我足为我。且空得之宝。不知其为祥也。曰有理哉翁言也。翁本生长于此乎。曰否。故乡礼安也。姓金也。他无可言者。在英肃然起慕曰金老不屑于今之世而隐于下流。终身穷饿。不易其操者也。彼欺人取物。切切然恐人知者。视此等人此等事。得不汗怍于中夜虚明之时乎。虽然向非王父亲访扣讯。则吾未知其果对人自道。使世之人。知有此事也。古钱
西厓集记崇宁通宝。活斋集记元丰通宝。贵古物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4L 页
 之可徵也。近年通用华钱之时。往往得古钱。开元,乾元唐也。皇宋,圣宋,至道,咸平,祥符,景德,天圣,明道,景佑,至和,嘉祐,治平,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元符,大观,政和宋也。景定南宋也。洪武,嘉靖,万历,天启,崇祯明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胡皇历代也。正隆金也。东国,朝鲜我东钱也。其馀大和,绍统,利用,景兴,昭武,景盛,光中,洪化,嘉隆,昭统,景熙,景求,宽永及古钱四五叶。并未考。或曰蒙古钱。或曰日本钱。盖天下古今之宝。萃于我东。亦一气数也。惟岭南不用胡钱。故余所得仅若干。姑记之。更俟博古者。
之可徵也。近年通用华钱之时。往往得古钱。开元,乾元唐也。皇宋,圣宋,至道,咸平,祥符,景德,天圣,明道,景佑,至和,嘉祐,治平,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元符,大观,政和宋也。景定南宋也。洪武,嘉靖,万历,天启,崇祯明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胡皇历代也。正隆金也。东国,朝鲜我东钱也。其馀大和,绍统,利用,景兴,昭武,景盛,光中,洪化,嘉隆,昭统,景熙,景求,宽永及古钱四五叶。并未考。或曰蒙古钱。或曰日本钱。盖天下古今之宝。萃于我东。亦一气数也。惟岭南不用胡钱。故余所得仅若干。姑记之。更俟博古者。画兰说
兰似贤。贤者不可多得。得见兰斯可矣。东国无真兰。惟有蕙似兰。且其质不似松竹。秋冬之后。不可得见。于是乎好事者画而见之。然善画亦不可多得也。余与松京朴子厚未及相见而知其贤。子厚亦疑余似贤。手画兰投示六幅。一本右抽。一本左抽。并蔼然如独行之士。一本在绝壁上。一本立恶木傍。一本秀凡卉中。并竦然自励。不渝其香。一本兰之族而亦可赏。殆东国所产蕙之类乎。出一手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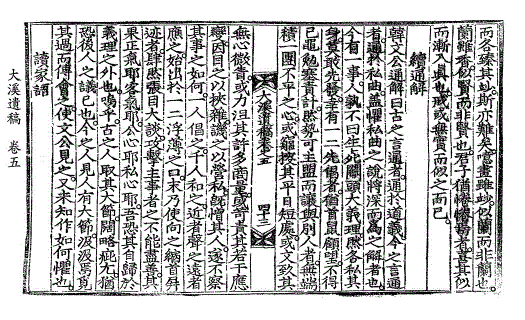 而各臻其妙。斯亦难矣。噫画虽妙。似兰而非兰也。兰虽香。似贤而非贤也。君子犹惓惓焉者。喜其似而渐入真也。戒或无实而似之而已。
而各臻其妙。斯亦难矣。噫画虽妙。似兰而非兰也。兰虽香。似贤而非贤也。君子犹惓惓焉者。喜其似而渐入真也。戒或无实而似之而已。续通解
韩文公通解曰古之言通者。通于道义。今之言通者。通于私曲。盖惧私曲之说将深而为之解者也。今有一事。人孰不曰生死关头大义理。然各私其身。莫敢先发。幸有一二先倡者。犹首鼠顾望。不得已黾勉塞责计。然势可主盟而让与别人者。无端积一团不平之心。或穷搜其平日短处。或文致其无心微眚。或力沮其许多商量。或苛责其若干应变。因目之以挟杂。讥之以营私。既憎其人。遂不察其事之如何。一人倡之。千人和之。近者声之远者应之。始出于一二浮薄之口。末乃使向之缩首屏迹者。肆然张目大谈。攻击主事者之不能尽善。其果正气耶客气耶。公心耶私心耶。吾恐其自归于义理之外也。呜乎。古之人取其大节。阔略疵尤。犹恐后人之议己也。今之人见人有大节。汲汲焉觅其过而傅会之。使文公见之。又未知作如何惧也。
读家语
大溪遗稿卷之五 第 7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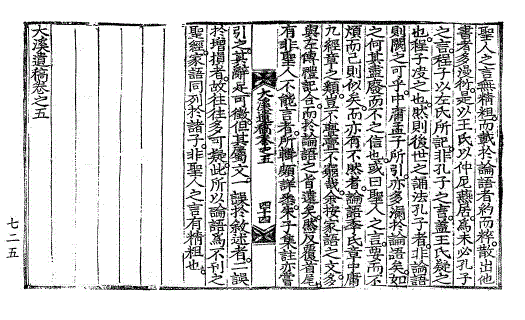 圣人之言无精粗。而载于论语者约而粹。散出他书者多漫衍。是以王氏以仲尼燕居。为未必孔子之言。程子以左氏所记。非孔子之言。盖王氏疑之也。程子决之也。然则后世之诵法孔子者。非论语则阙之可乎。中庸孟子所引。亦多漏于论语矣。如之何其尽废而不之信也。或曰圣人之言。要而不烦而已则似矣。而亦有不然者。论语季氏章中庸九经章之类。岂不亹亹不穷哉。余按家语之文。多与左传礼记合。而于论语之旨远矣。然反覆首尾。有非圣人不能言者。所辑颇详悉。朱子集注亦尝引之。其辞足可徵。但其属文。一误于叙述者。二误于增损者。故往往多可疑。此所以论语为不刊之圣经。家语同列于诸子。非圣人之言有精粗也。
圣人之言无精粗。而载于论语者约而粹。散出他书者多漫衍。是以王氏以仲尼燕居。为未必孔子之言。程子以左氏所记。非孔子之言。盖王氏疑之也。程子决之也。然则后世之诵法孔子者。非论语则阙之可乎。中庸孟子所引。亦多漏于论语矣。如之何其尽废而不之信也。或曰圣人之言。要而不烦而已则似矣。而亦有不然者。论语季氏章中庸九经章之类。岂不亹亹不穷哉。余按家语之文。多与左传礼记合。而于论语之旨远矣。然反覆首尾。有非圣人不能言者。所辑颇详悉。朱子集注亦尝引之。其辞足可徵。但其属文。一误于叙述者。二误于增损者。故往往多可疑。此所以论语为不刊之圣经。家语同列于诸子。非圣人之言有精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