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延平答问质疑
延平答问质疑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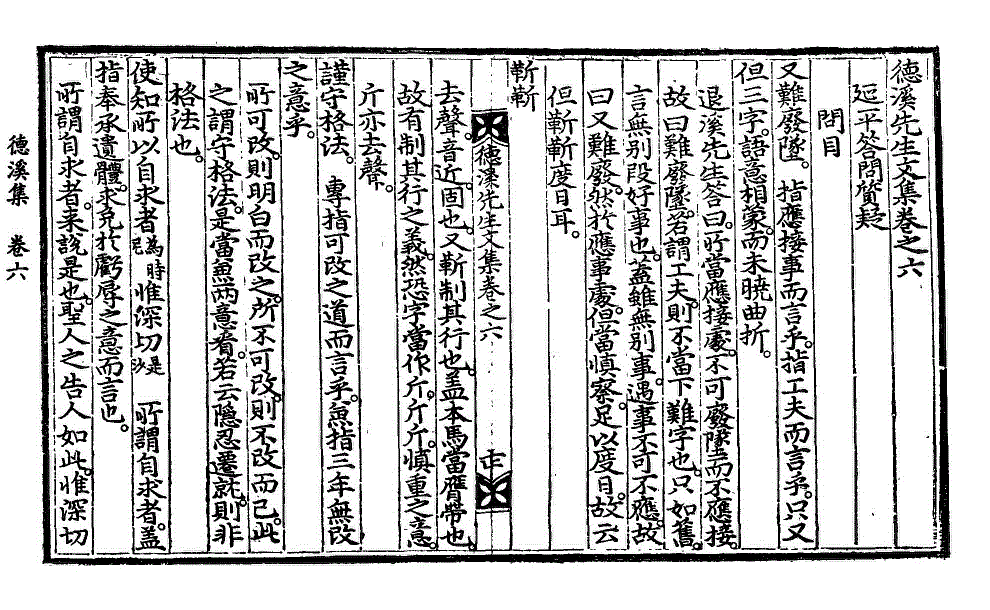 问目
问目又难废坠。 指应接事而言乎。指工夫而言乎。只又但三字。语意相蒙。而未晓曲折。
退溪先生答曰。所当应接处。不可废坠而不应接。故曰难废坠。若谓工夫。则不当下难字也。只如旧。言无别段好事也。盖虽无别事。遇事不可不应。故曰又难废。然于应事处。但当慎察。足以度日。故云但靳靳度日耳。
靳靳
去声。音近。固也。又靳制其行也。盖本马当膺带也。故有制其行之义。然恐字当作斤。斤斤。慎重之意。斤亦去声。
谨守格法。 专指可改之道而言乎。兼指三年无改之意乎。
所可改。则明白而改之。所不可改。则不改而已。此之谓守格法。是当兼两意看。若云隐忍迁就。则非格法也。
使知所以自求者(为时尼)惟深切(是沙) 所谓自求者。盖指奉承遗体。求免于亏辱之意而言也。
所谓自求者。来说是也。圣人之告人如此。惟深切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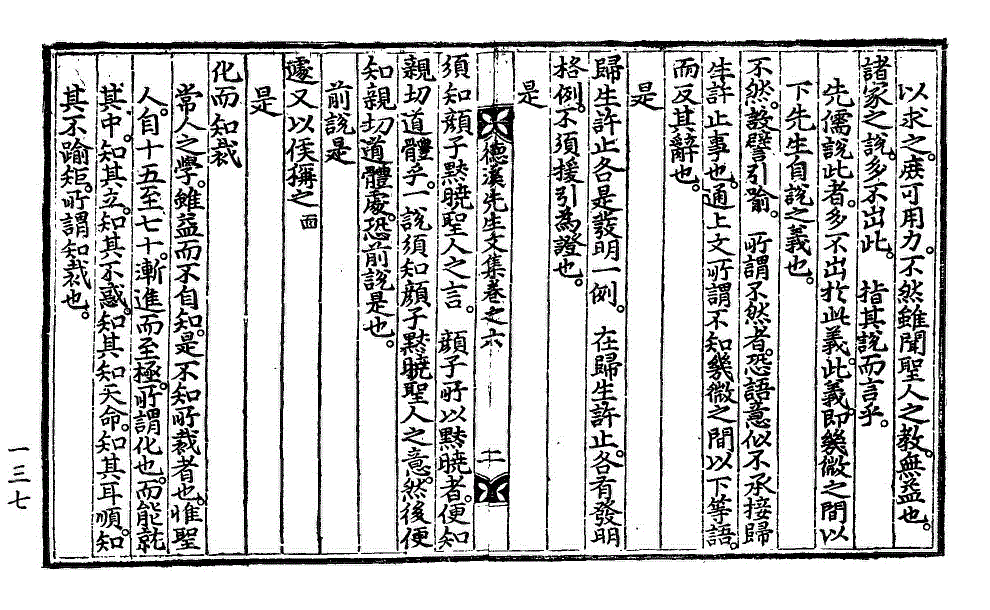 以求之。庶可用力。不然虽闻圣人之教。无益也。
以求之。庶可用力。不然虽闻圣人之教。无益也。诸家之说。多不出此。 指其说而言乎。
先儒说此者。多不出于此义。此义。即几微之间以下先生自说之义也。
不然。设譬引喻。 所谓不然者。恐语意似不承接归生,许止事也。通上文所谓不知几微之间以下等语。而反其辞也。
是
归生,许止各是发明一例。 在归生,许止。各有发明格例。不须援引为證也。
是
须知颜子默晓圣人之言。 颜子所以默晓者。便知亲切道体乎。一说须知颜子默晓圣人之意。然后便知亲切道体处。恐前说是也。
前说是
遽又以侯称之(面)
是
化而知裁
常人之学。虽益而不自知。是不知所裁者也。惟圣人。自十五至七十。渐进而至极。所谓化也。而能就其中。知其立。知其不惑。知其知天命。知其耳顺。知其不踰矩。所谓知裁也。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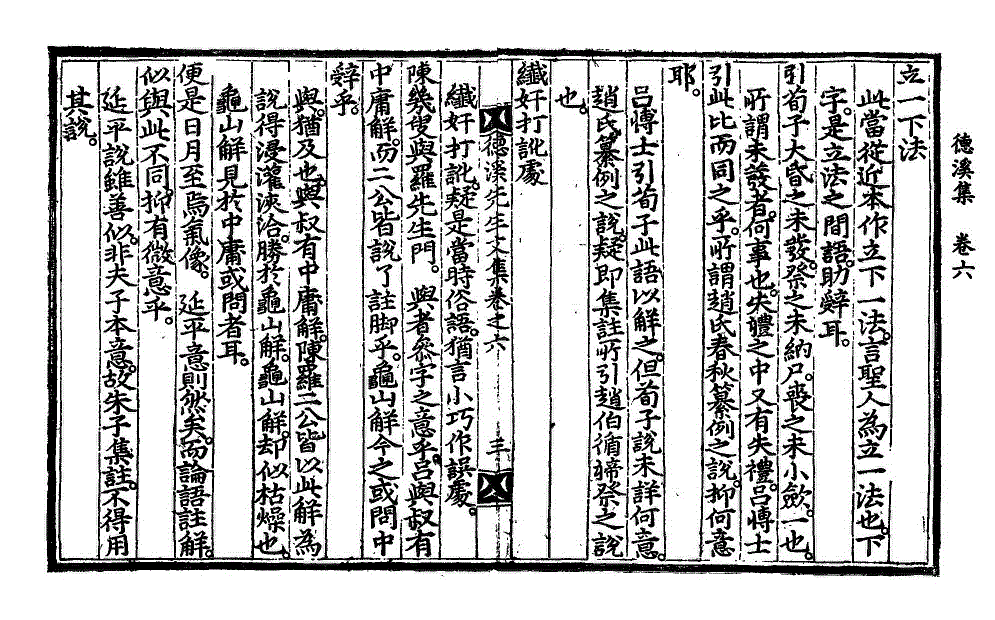 立一下法
立一下法此当从近本作立下一法。言圣人为立一法也。下字。是立法之间语。助辞耳。
引荀子大昏之未发。祭之未纳尸。丧之未小敛。一也。
所谓未发者。何事也。失礼之中又有失礼。吕博士
引此比而同之乎。所谓赵氏春秋纂例之说。抑何意耶。
吕博士引荀子此语以解之。但荀子说未详何意。赵氏纂例之说。疑即集注所引赵伯循禘祭之说也。
纤奸打讹处
纤奸打讹。疑是当时俗语。犹言小巧作误处。
陈几叟与罗先生门。 与者参字之意乎。吕与叔有中庸解。而二公皆说了注脚乎。龟山解今之或问中辞乎。
与。犹及也。与叔有中庸解。陈,罗二公皆以此解为说得浸灌浃洽。胜于龟山解。龟山解。却似枯燥也。龟山解见于中庸或问者耳。
便是日月至焉气像。 延平意则然矣。而论语注解。似与此不同。抑有微意乎。
延平说虽善似。非夫子本意。故朱子集注。不得用其说。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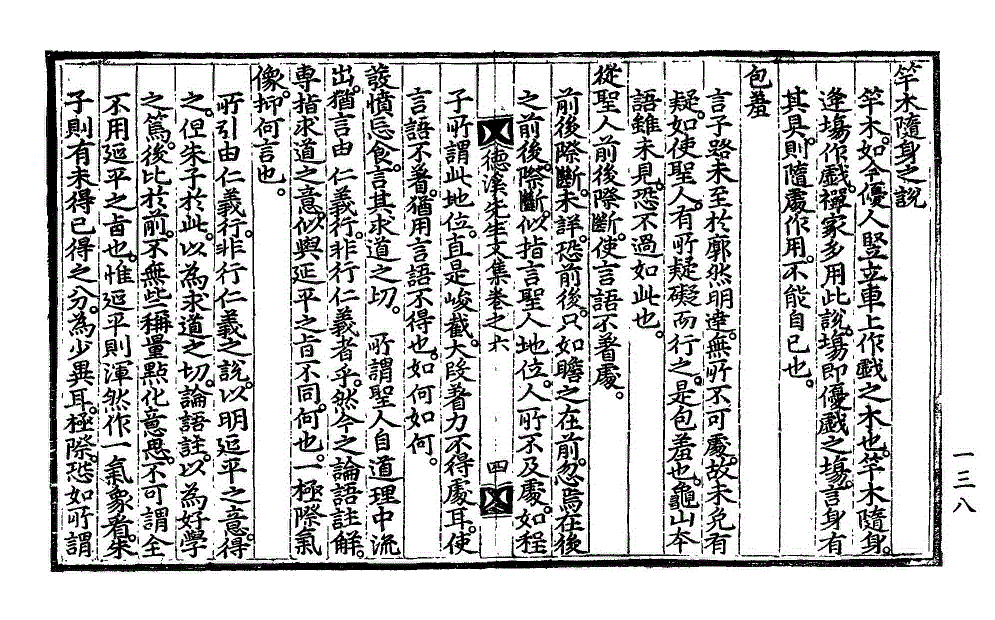 竿木随身之说
竿木随身之说竿木。如今优人竖立车上作戏之木也。竿木随身。逄场作戏。禅家多用此说。场即优戏之场。言身有其具。则随处作用。不能自已也。
包羞
言子路未至于廓然明达。无所不可处。故未免有疑。如使圣人。有所疑碍而行之。是包羞也。龟山本语虽未见。恐不过如此也。
从圣人前后际断。使言语不着处。
前后际断。未详。恐前后只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前后。际断。似指言圣人地位。人所不及处。如程子所谓此地位。直是峻截。大段着力不得处耳。使言语不着。犹用言语不得也。如何如何。
发愤忘食。言其求道之切。 所谓圣人自道理中流出。犹言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者乎。然今之论语注解。专指求道之意。似与延平之旨不同。何也。一极际气像。抑何言也。
所引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之说。以明延平之意。得之。但朱子于此。以为求道之切。论语注。以为好学之笃。后比于前。不无些称量点化意思。不可谓全不用延平之旨也。惟延平则浑然作一气象看。朱子则有未得已得之分。为少异耳。极际。恐如所谓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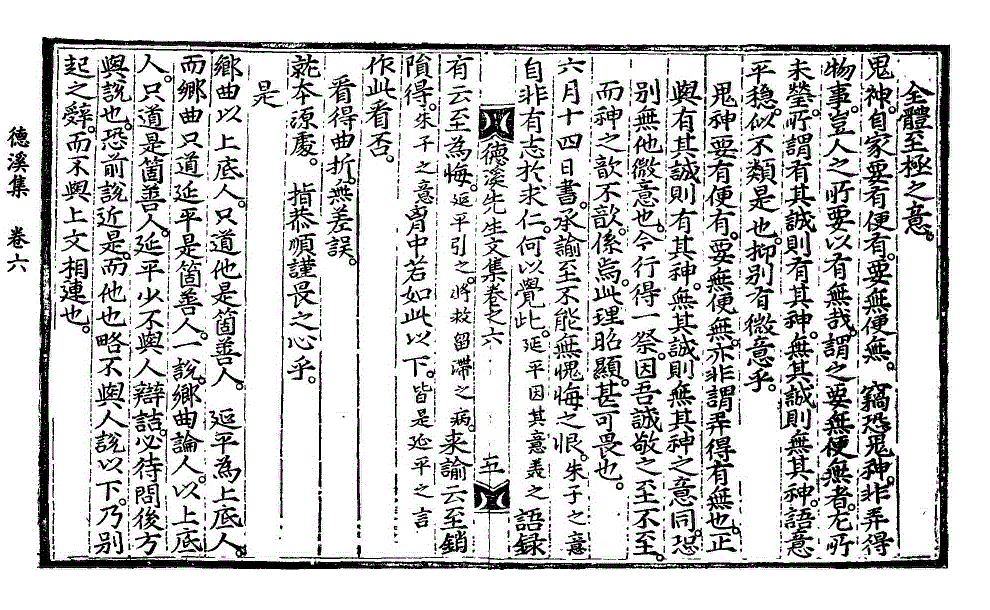 全体至极之意。
全体至极之意。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无便无。 窃恐鬼神。非弄得物事。岂人之所要以有无哉。谓之要无便无者。尤所未莹。所谓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语意平稳。似不类是也。抑别有微意乎。
鬼神要有便有。要无便无。亦非谓弄得有无也。正与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之意同。恐别无他微意也。今行得一祭。因吾诚敬之至不至。而神之歆不歆。系焉。此理昭显。甚可畏也。
六月十四日书。承谕至不能无愧悔之恨。(朱子之意)自非有志于求仁。何以觉此。(延平因其意美之)语录有云至为悔。(延平引之。将救留滞之病。)来谕云至销陨得。(朱子之意)胸中若如此以下。(皆是延平之言) 作此看否。
看得曲折。无差误。
就本源处。 指恭顺谨畏之心乎。
是
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 延平为上底人。而乡曲只道延平是个善人。一说。乡曲论人。以上底人。只道是个善人。延平少不与人辩诘。必待问后方与说也。恐前说近是。而他也略不与人说以下。乃别起之辞。而不与上文相连也。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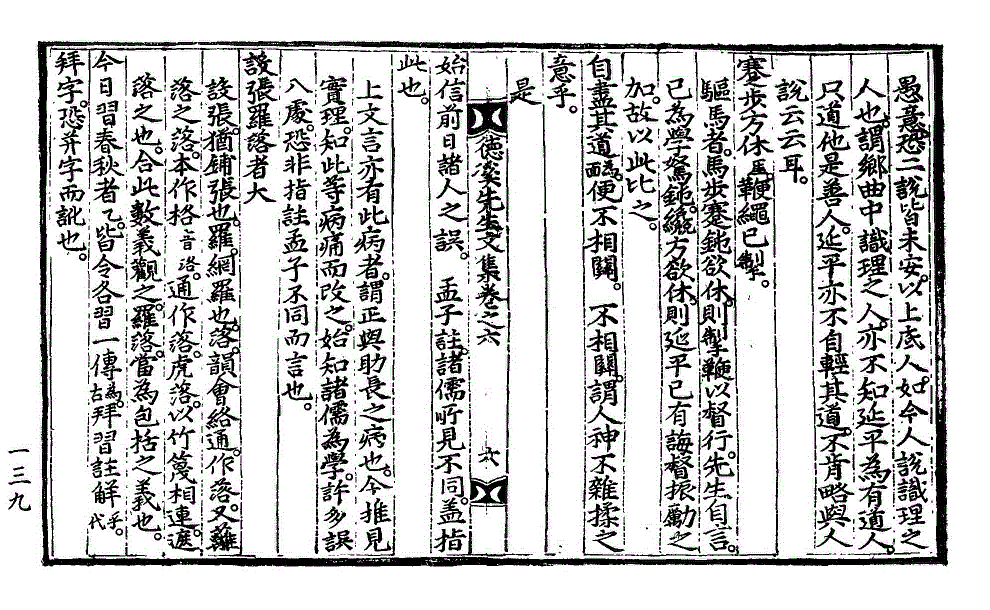 愚意。恐二说皆未安。以上底人。如今人说识理之人也。谓乡曲中识理之人。亦不知延平为有道人。只道他是善人。延平亦不自轻其道。不肯略与人说云云耳。
愚意。恐二说皆未安。以上底人。如今人说识理之人也。谓乡曲中识理之人。亦不知延平为有道人。只道他是善人。延平亦不自轻其道。不肯略与人说云云耳。蹇步方休(厓)。鞭绳已掣。
驱马者。马步蹇钝欲休。则掣鞭以督行。先生自言。已为学驽钝。才方欲休。则延平已有诲督振励之加。故以此比之。
自尽其道。(为面)便不相关。 不相关。谓人神不杂揉之意乎。
是
始信前日诸人之误。 孟子注。诸儒所见不同。盖指此也。
上文言亦有此病者。谓正与助长之病也。今推见实理。知此等病痛而改之。始知诸儒为学。许多误入处。恐非指注孟子不同而言也。
设张罗落者大
设张。犹铺张也。罗。网罗也。落。韵会络通。作落。又蓠落之落。本作格。(音洛)通作落。虎落。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合此数义观之。罗落。当为包括之义也。
今日习春秋者。(乙)皆令各习一传。(为古)拜习注解。(乎代)拜字。恐并字而讹也。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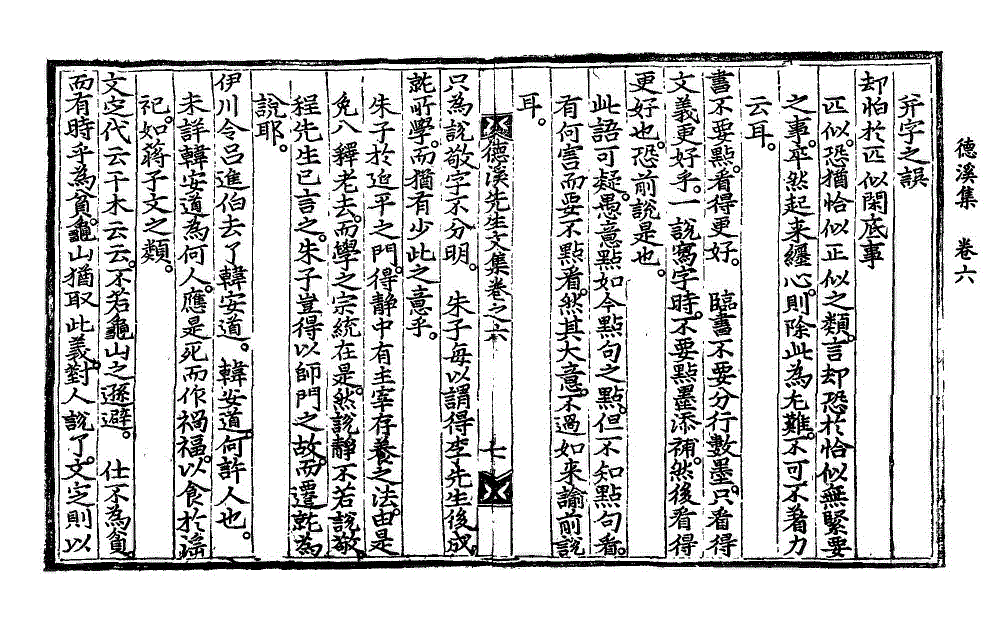 并字之误
并字之误却怕于匹似闲底事
匹似。恐犹恰似正似之类。言却恐于恰似无紧要之事。卒然起来缠心。则除此为尤难。不可不着力云耳。
书不要点。看得更好。 临书不要分行数墨。只看得文义更好乎。一说写字时。不要点墨添补。然后看得更好也。恐前说是也。
此语可疑。愚意点如今点句之点。但不知点句看。有何害而要不点看。然其大意。不过如来谕前说耳。
只为说敬字不分明。 朱子每以谓得李先生后成就所学。而犹有少此之意乎。
朱子于延平之门。得静中有主宰存养之法。由是免入释老去。而学之宗统在是。然说静不若说敬程先生已言之。朱子岂得以师门之故。而迁就为说耶。
伊川令吕进伯去了韩安道。 韩安道。何许人也。
未详韩安道为何人。应是死而作祸福。以食于淫祀。如蒋子文之类。
文定代云干木云云。不若龟山之逊避。 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龟山犹取此义。对人说了。文定则以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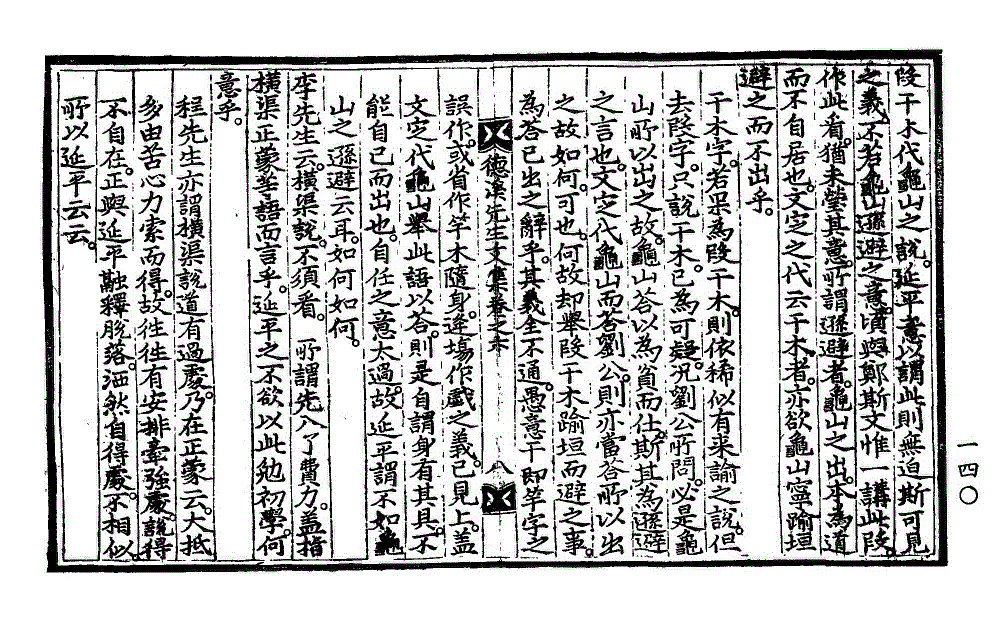 段干木代龟山之说。延平意以谓此则无迫斯可见之义。不若龟山逊避之意。顷与郑斯文惟一讲此段。作此看。犹未莹其意。所谓逊避者。龟山之出。本为道而不自居也。文定之代云干木者。亦欲龟山宁踰垣避之而不出乎。
段干木代龟山之说。延平意以谓此则无迫斯可见之义。不若龟山逊避之意。顷与郑斯文惟一讲此段。作此看。犹未莹其意。所谓逊避者。龟山之出。本为道而不自居也。文定之代云干木者。亦欲龟山宁踰垣避之而不出乎。干木字。若果为段干木。则依稀似有来谕之说。但去段字。只说干木。已为可疑。况刘公所问。必是龟山所以出之故。龟山答以为贫而仕。斯其为逊避之言也。文定代龟山而答刘公。则亦当答所以出之故如何。可也。何故却举段干木踰垣而避之事。为答已出之辞乎。其义全不通。愚意干即竿字之误作。或省作竿木随身。逄场作戏之义。已见上。盖文定代龟山举此语以答。则是自谓身有其具。不能自己而出也。自任之意太过。故延平谓不如龟山之逊避云耳。如何如何。
李先生云。横渠说。不须看。 所谓先入了费力。盖指横渠正蒙等语而言乎。延平之不欲以此勉初学。何意乎。
程先生亦谓横渠说道有过处。乃在正蒙云。大抵多由苦心力索而得。故往往有安排牵强处。说得不自在。正与延平融释脱落。洒然自得处。不相似。所以延平云云。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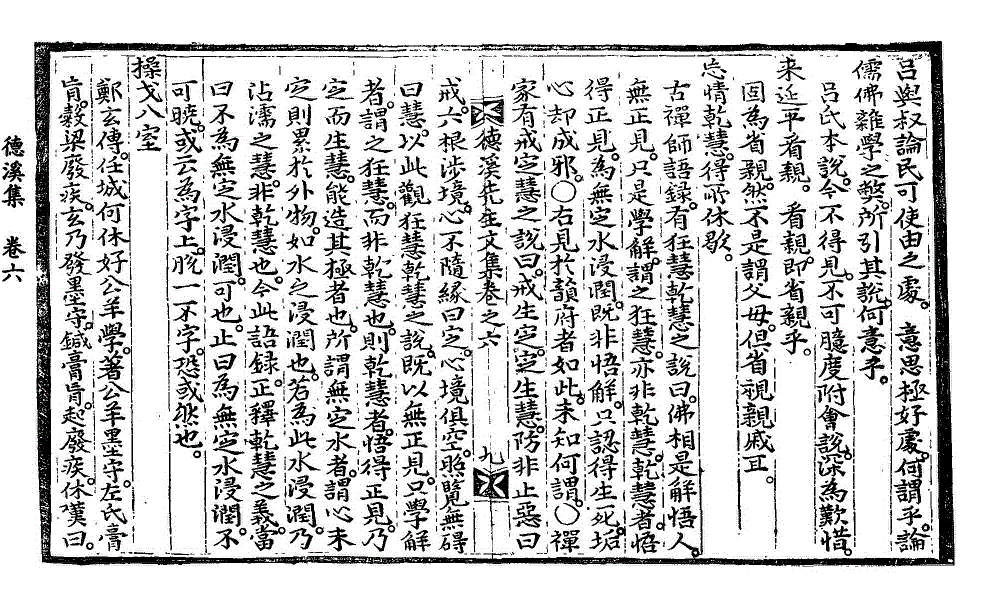 吕与叔论民可使由之处。 意思极好处。何谓乎。论儒佛杂学之弊。所引其说。何意乎。
吕与叔论民可使由之处。 意思极好处。何谓乎。论儒佛杂学之弊。所引其说。何意乎。吕氏本说。今不得见。不可臆度附会说。深为叹惜。
来延平看亲。 看亲。即省亲乎。
固为省亲。然不是谓父母。但省视亲戚耳。
忘情乾慧。得所休歇。
古禅师语录。有狂慧乾慧之说曰。佛相是解悟人。无正见。只是学解。谓之狂慧。亦非乾慧。乾慧者。悟得正见。为无定水浸润。既非悟解。只认得生死。垢心却成邪。○右见于韵府者如此。未知何谓。○禅家有戒定慧之说曰。戒生定。定生慧。防非止恶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随缘曰定。心境俱空。照览无碍曰慧。以此观狂慧乾慧之说。既以无正见。只学解者。谓之狂慧。而非乾慧也。则乾慧者。悟得正见。乃定而生慧。能造其极者也。所谓无定水者。谓心未定则累于外物。如水之浸润也。若为此水浸润。乃沾濡之慧。非乾慧也。今此语录。正释乾慧之义。当曰不为无定水浸润。可也。止曰为无定水浸润。不可晓。或云为字上。脱一不字。恐或然也。
操戈入室
郑玄传。任城何休好公羊学。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叹曰。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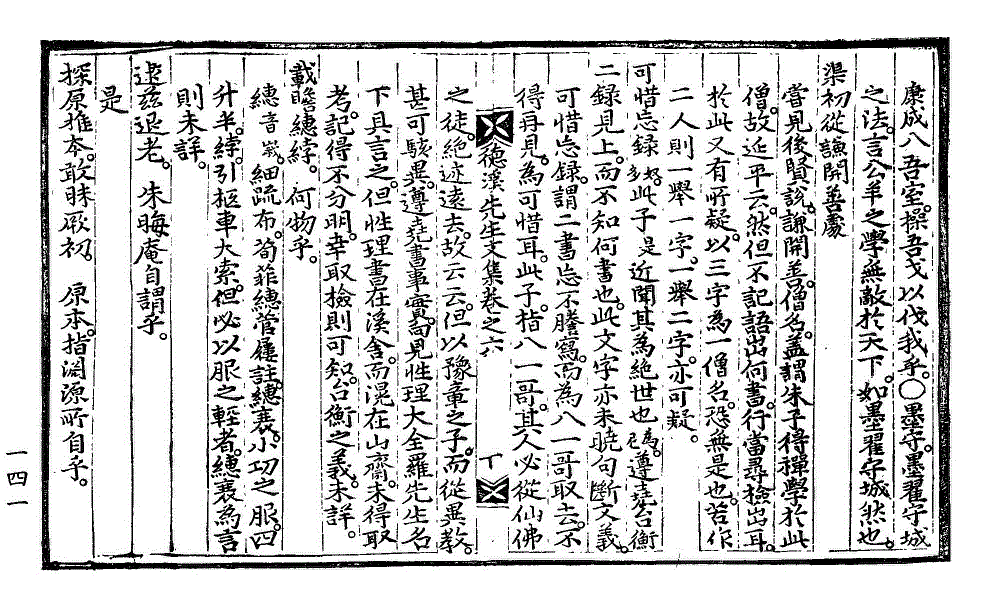 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墨守。墨翟守城之法。言公羊之学无敌于天下。如墨翟守城然也。
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墨守。墨翟守城之法。言公羊之学无敌于天下。如墨翟守城然也。渠初从谦开善处
尝见后贤说。谦开善。僧名。盖谓朱子得禅学于此僧。故延平云。然但不记语出何书。行当寻检出耳。于此又有所疑。以三字为一僧名。恐无是也。若作二人则一举一字。一举二字。亦可疑。
可惜忘录(奴多)。此子(是)近闻其为绝世也(为尼)。遵尧,台衡二录见上。而不知何书也。此文字亦未晓句断文义。
可惜忘录。谓二书忘不誊写。而为八一哥取去。不得再见。为可惜耳。此子。指八一哥。其人必从仙佛之徒。绝迹远去。故云云。但以豫章之子。而从异教。甚可骇异。遵尧书事实。向见性理大全罗先生名下具言之。但性理书在溪舍。而滉在山斋。未得取考。记得不分明。幸取检则可知。台衡之义。未详。
载瞻繐綍。 何物乎。
繐(音岁)。细疏布。荀菲繐管屦注。繐衰。小功之服。四升半。綍。引柩车大索。但必以服之轻者。繐衰为言则未详。
逮玆退老。 朱晦庵自谓乎。
是
探原推本。敢昧厥初。 原本。指渊源所自乎。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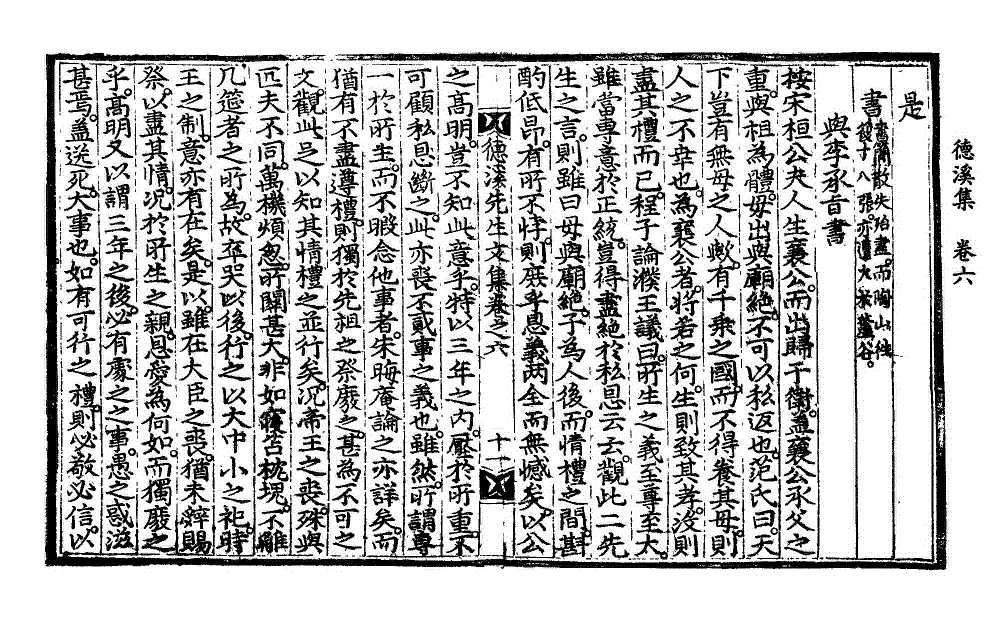 是
是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书(书简散失殆尽。而陶山往复十八张。亦遭火于芦谷。)
与李承旨书
按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于卫。尽襄公承父之重。与祖为体。母出与庙绝。不可以私返也。范氏曰。天下岂有无母之人欤。有千乘之国。而不得养其母。则人之不幸也。为襄公者。将若之何。生则致其孝。没则尽其礼而已。程子论濮王议曰。所生之义至尊至大。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云云。观此二先生之言。则虽曰母与庙绝。子为人后。而情礼之间。斟酌低昂。有所不悖。则庶乎恩义两全而无憾矣。以公之高明。岂不知此意乎。特以三年之内。压于所重。不可顾私恩断之。此亦丧不贰事之义也。虽然。所谓专一于所主。而不暇念他事者。朱晦庵论之亦详矣。而犹有不尽遵礼。则独于先祖之祭废之。甚为不可之文。观此足以知其情礼之并行矣。况帝王之丧。殊与匹夫不同。万机烦匆。所关甚大。非如寝苫枕块。不离几筵者之所为。故卒哭以后。行之以大中小之祀。时王之制。意亦有在矣。是以。虽在大臣之丧。犹未辞赐祭。以尽其情。况于所生之亲。恩爱为何如。而独废之乎。高明又以谓三年之后。必有处之之事。愚之惑滋甚焉。盖送死。大事也。如有可行之礼。则必敬必信。以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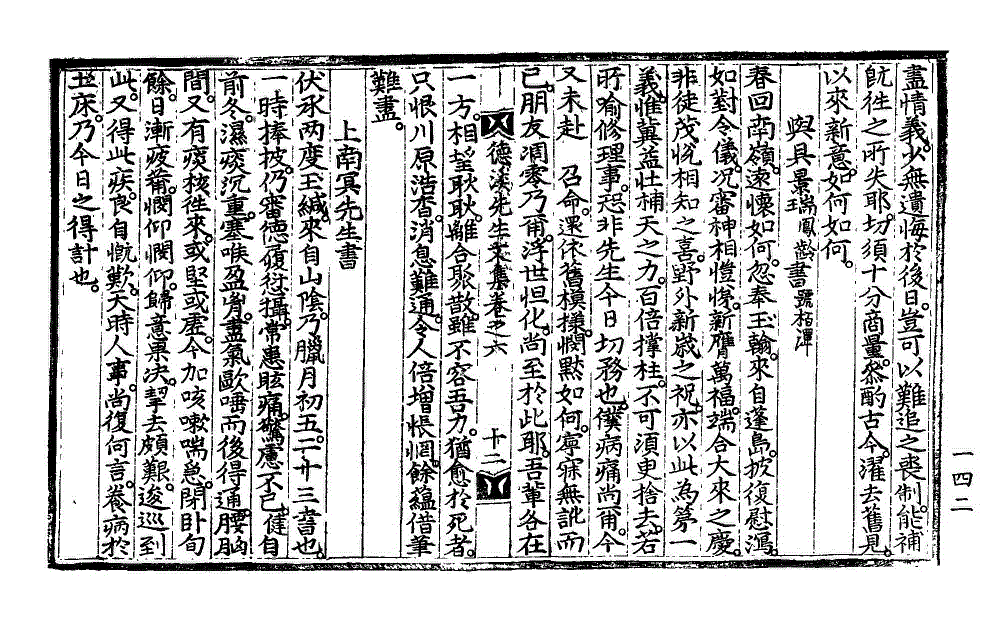 尽情义。少无遗悔于后日。岂可以难追之丧制。能补既往之所失耶。切须十分商量。参酌古今。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如何如何。
尽情义。少无遗悔于后日。岂可以难追之丧制。能补既往之所失耶。切须十分商量。参酌古今。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如何如何。与具景瑞(凤龄)书(号柏潭)
春回南岭。远怀如何。忽奉玉翰。来自蓬岛。披复慰泻。如对令仪。况审神相恺悌。新膺万福。端合大来之庆。非徒茂悦相知之喜。野外新岁之祝。亦以此为第一义。惟冀益壮补天之力。百倍撑柱。不可须臾舍去。若所喻修理事。恐非先生今日切务也。仆病痛尚尔。今又未赴 召命。还依旧模样。悯默如何。宁寐无讹而已。朋友凋零乃尔。浮世怛化。尚至于此耶。吾辈各在一方。相望耿耿。离合聚散。虽不容吾力。犹愈于死者。只恨川原浩杳。消息难通。令人倍增怅惘。馀蕴借笔难尽。
上南冥先生书
伏承两度玉缄。来自山阴。乃腊月初五。二十三书也。一时捧披。仍审德履愆摄。常患眩痛。惊虑不已。健自前冬。湿痰沈重。塞喉盈胸。尽气欧唾而后得通。腰胸间。又有痰核往来。或坚或虚。今加咳嗽喘急。闭卧旬馀。日渐疲薾。悯仰悯仰。归意果决。挈去颇艰。逡巡到此。又得此疾。良自慨叹。天时人事。尚复何言。养病于土床。乃今日之得计也。
与林葛川书(名薰)
献岁发春。想惟新禧益茂。遥贺万万。生添齿以来。眩晕增剧。无稍平时节。亦衰境常理。奈何。只以离索相远。无便奉话。常为耿耿耳。今者县城主在丧。适因下人往。聊达鄙情。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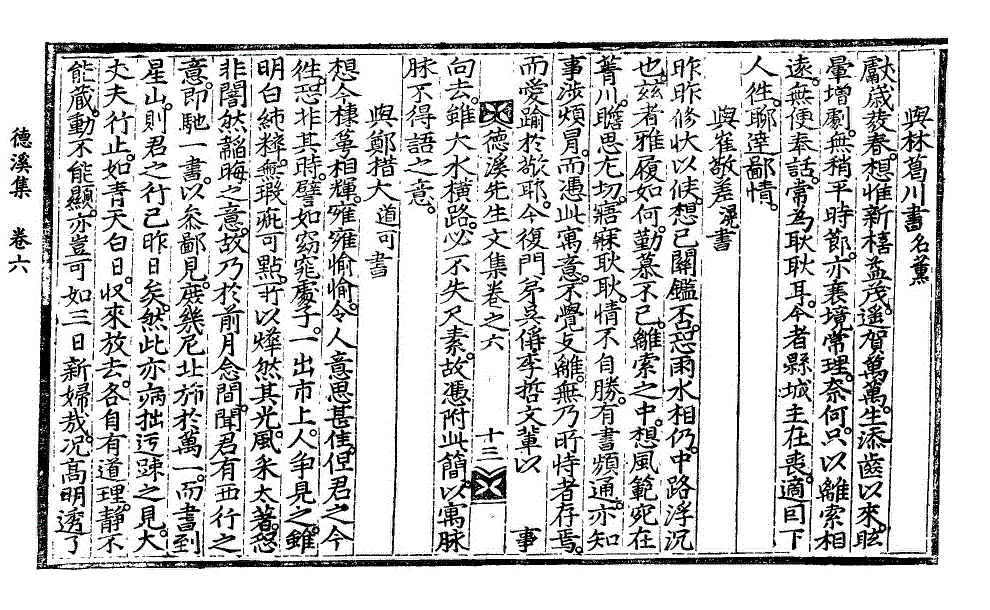 与崔敬差(滉)书
与崔敬差(滉)书昨昨修状以候。想已关鉴否。恐雨水相仍。中路浮沈也。玆者雅履如何。勤慕不已。离索之中。想风范宛在菁川。瞻思尤切。寤寐耿耿。情不自胜。有书频通。亦知事涉烦冒。而凭此寓意。不觉支离。无乃所恃者存焉。而爱踰于敬耶。今复门弟吴称,李哲文辈以 事向去。虽大水横路。必不失尺素。故凭附此简。以寓脉脉不得语之意。
与郑措大(道可)书
想今棣萼相辉。雍雍愉愉。令人意思甚佳。但君之今往。恐非其时。譬如窈窕处子。一出市上。人争见之。虽明白纯粹。无瑕疵可点。所以烨然其光。风采太著。恐非闇然韬晦之意。故乃于前月念间。闻君有西行之意。即驰一书。以参鄙见。庶几尼北旆于万一。而书到星山。则君之行已昨日矣。然此亦病拙迂疏之见。大丈夫行止。如青天白日。收来放去。各自有道理。静不能藏。动不能显。亦岂可如三日新妇哉。况高明透了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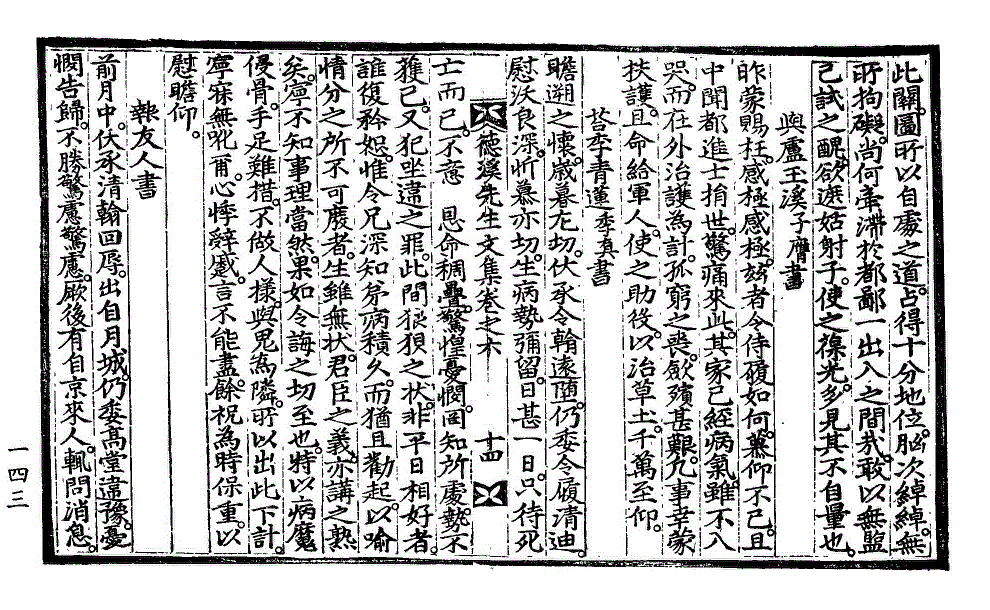 此关。图所以自处之道。占得十分地位。胸次绰绰。无所拘碍。尚何牵滞于都鄙一出入之间哉。敢以无盐已试之丑。欲遮姑射子。使之葆光。多见其不自量也。
此关。图所以自处之道。占得十分地位。胸次绰绰。无所拘碍。尚何牵滞于都鄙一出入之间哉。敢以无盐已试之丑。欲遮姑射子。使之葆光。多见其不自量也。与卢玉溪(子膺)书
昨蒙赐枉。感极感极。玆者令侍履如何。慕仰不已。且中闻都进士捐世。惊痛来此。其家已经病气。虽不入哭。而在外治护为计。孤穷之丧。敛殡甚艰。凡事幸蒙扶护。且命给军人。使之助役。以治草土。千万至仰。
答李青莲(季真)书
瞻溯之怀。岁暮尤切。伏承令翰远堕。仍委令履清迪。慰沃良深。忻慕亦切。生病势弥留。日甚一日。只待死亡而已。不意 恩命稠叠。惊惶忧悯。罔知所处。势不获已。又犯坐违之罪。此间狼狈之状。非平日相好者。谁复矜恕。惟令兄深知弟病积久。而犹且劝起。以喻情分之所不可废者。生虽无状。君臣之义。亦讲之熟矣。宁不知事理当然。果如令诲之切至也。特以病魔侵骨。手足难措。不做人样。与鬼为邻。所以出此下计。宁寐无吪尔。心悸辞蹙。言不能尽。馀祝为时保重。以慰瞻仰。
报友人书
前月中。伏承清翰回辱。出自月城。仍委高堂违豫。忧悯告归。不胜惊虑惊虑。厥后有自京来人。辄问消息。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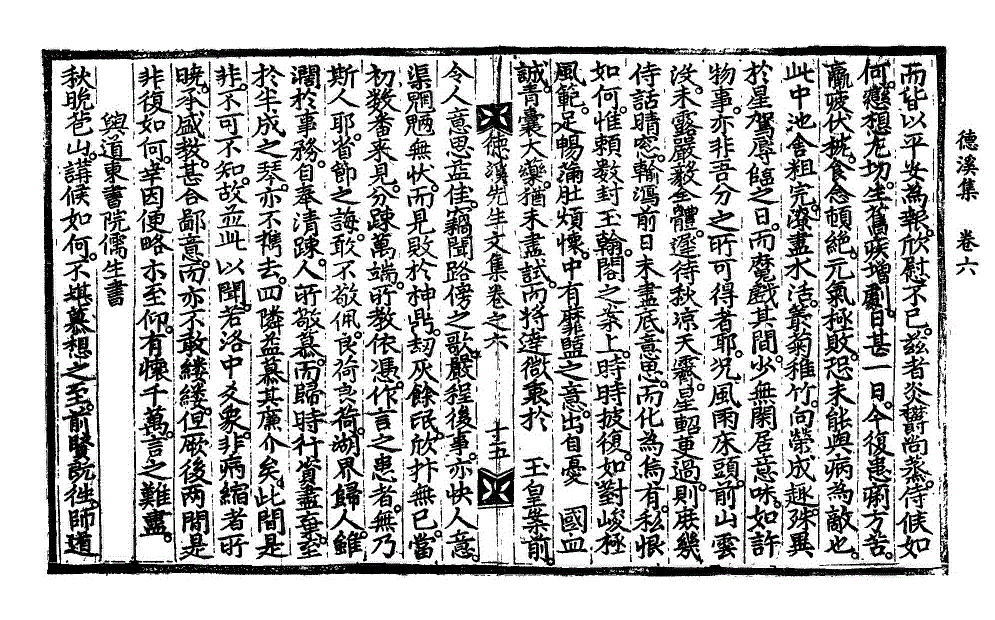 而皆以平安为报。欣慰不已。玆者炎郁尚蒸。侍候如何。恋想尤切。生旧疾增剧。日甚一日。今复患痢方苦。羸疲伏枕。食念顿绝。元气极败。恐未能与病为敌也。此中池舍粗完。潦尽水活。丛菊稚竹。向荣成趣。殊异于星驾辱临之日。而魔戏其间。少无闲居意味。如许物事。亦非吾分之所可得者耶。况风雨床头。前山云没。未露严毅全体。迟待秋凉天霁。星轺更过。则庶几侍话晴窗。输泻前日未尽底意思。而化为乌有。私恨如何。惟赖数封玉翰。阁之案上。时时披复。如对峻极风范。足畅满肚烦怀。中有靡盬之意。出自忧 国血诚。青囊大药。犹未尽试。而将达微衷于 玉皇案前。令人意思益佳。窃闻路傍之歌。严程后事。亦快人意。渠魍魉无状。而见败于神鼎。劫灰馀氓。欣抃无已。当初数番来见。分疏万端。所教依凭。作言之患者。无乃斯人耶。省节之诲。敢不敬佩。良荷良荷。湖界归人。虽阔于事务。自奉清疏。人所敬慕。而归时行资尽弃。至于半成之琴。亦不携去。四邻益慕其廉介矣。此间是非。不可不知。故并此以闻。若洛中爻象。非病缩者所晓。承盛教。甚合鄙意。而亦不敢缕缕。但厥后两间是非复如何。幸因便略示至仰。有怀千万。言之难尽。
而皆以平安为报。欣慰不已。玆者炎郁尚蒸。侍候如何。恋想尤切。生旧疾增剧。日甚一日。今复患痢方苦。羸疲伏枕。食念顿绝。元气极败。恐未能与病为敌也。此中池舍粗完。潦尽水活。丛菊稚竹。向荣成趣。殊异于星驾辱临之日。而魔戏其间。少无闲居意味。如许物事。亦非吾分之所可得者耶。况风雨床头。前山云没。未露严毅全体。迟待秋凉天霁。星轺更过。则庶几侍话晴窗。输泻前日未尽底意思。而化为乌有。私恨如何。惟赖数封玉翰。阁之案上。时时披复。如对峻极风范。足畅满肚烦怀。中有靡盬之意。出自忧 国血诚。青囊大药。犹未尽试。而将达微衷于 玉皇案前。令人意思益佳。窃闻路傍之歌。严程后事。亦快人意。渠魍魉无状。而见败于神鼎。劫灰馀氓。欣抃无已。当初数番来见。分疏万端。所教依凭。作言之患者。无乃斯人耶。省节之诲。敢不敬佩。良荷良荷。湖界归人。虽阔于事务。自奉清疏。人所敬慕。而归时行资尽弃。至于半成之琴。亦不携去。四邻益慕其廉介矣。此间是非。不可不知。故并此以闻。若洛中爻象。非病缩者所晓。承盛教。甚合鄙意。而亦不敢缕缕。但厥后两间是非复如何。幸因便略示至仰。有怀千万。言之难尽。与道东书院儒生书
秋晚苞山。讲候如何。不堪慕想之至。前贤既往。师道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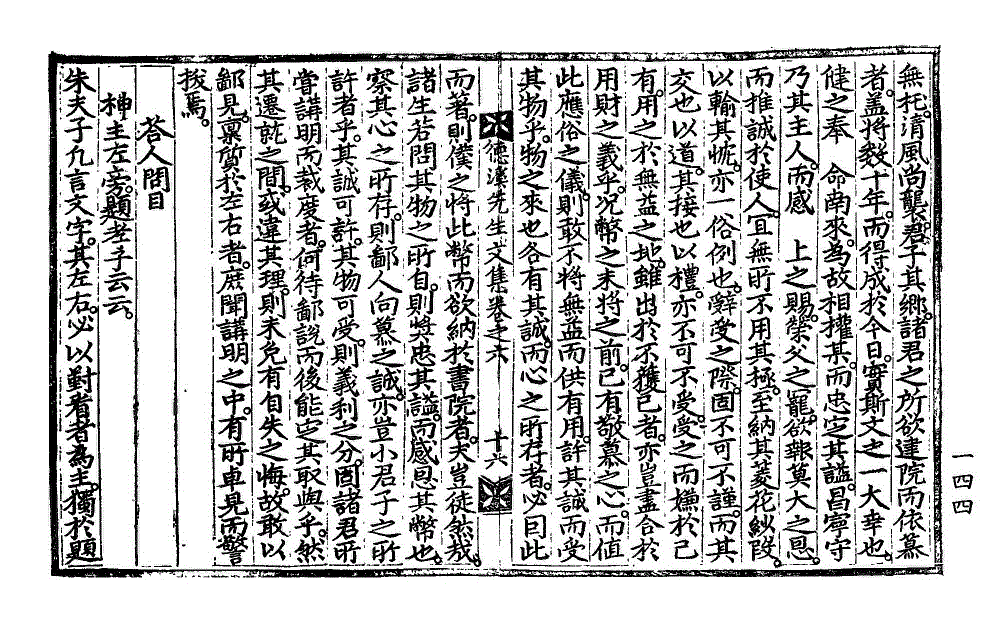 无托。清风尚袭。君子其乡。诸君之所欲建院而依慕者。盖将数十年。而得成于今日。实斯文之一大幸也。健之奉 命南来。为故相权某。而忠定其谥。昌宁守乃其主人。而感 上之赐。荣父之宠。欲报莫大之恩。而推诚于使人。宜无所不用其极。至纳其菱花纱段。以输其忱。亦一俗例也。辞受之际。固不可不谨。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亦不可不受。受之而嫌于己有。用之于无益之地。虽出于不获已者。亦岂尽合于用财之义乎。况币之未将之前。己有敬慕之心。而值此应俗之仪。则敢不将无益而供有用。许其诚而受其物乎。物之来也各有其诚。而心之所存者。必因此而著。则仆之将此币而欲纳于书院者。夫岂徒然哉。诸生若问其物之所自。则奖忠其谥。而感恩其币也。察其心之所存。则鄙人向慕之诚。亦岂小君子之所许者乎。其诚可许。其物可受。则义利之分。固诸君所尝讲明而裁度者。何待鄙说而后能定其取与乎。然其迁就之间。或违其理。则未免有自失之悔。故敢以鄙见。禀质于左右者。庶闻讲明之中。有所卓见而警拔焉。
无托。清风尚袭。君子其乡。诸君之所欲建院而依慕者。盖将数十年。而得成于今日。实斯文之一大幸也。健之奉 命南来。为故相权某。而忠定其谥。昌宁守乃其主人。而感 上之赐。荣父之宠。欲报莫大之恩。而推诚于使人。宜无所不用其极。至纳其菱花纱段。以输其忱。亦一俗例也。辞受之际。固不可不谨。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亦不可不受。受之而嫌于己有。用之于无益之地。虽出于不获已者。亦岂尽合于用财之义乎。况币之未将之前。己有敬慕之心。而值此应俗之仪。则敢不将无益而供有用。许其诚而受其物乎。物之来也各有其诚。而心之所存者。必因此而著。则仆之将此币而欲纳于书院者。夫岂徒然哉。诸生若问其物之所自。则奖忠其谥。而感恩其币也。察其心之所存。则鄙人向慕之诚。亦岂小君子之所许者乎。其诚可许。其物可受。则义利之分。固诸君所尝讲明而裁度者。何待鄙说而后能定其取与乎。然其迁就之间。或违其理。则未免有自失之悔。故敢以鄙见。禀质于左右者。庶闻讲明之中。有所卓见而警拔焉。答人问目
神主左旁。题孝子云云。
朱夫子凡言文字。其左右。必以对看者为主。独于题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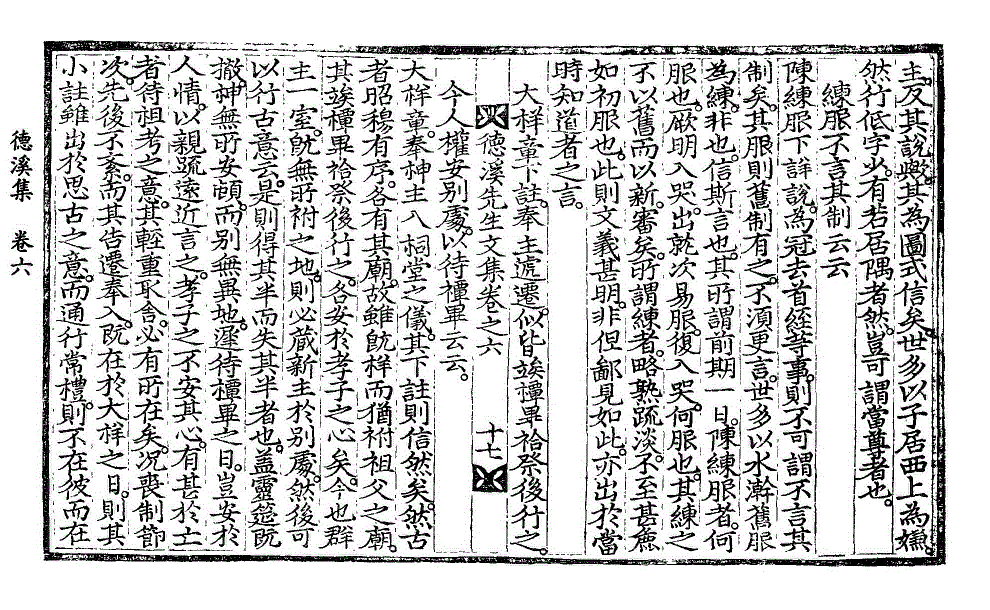 主。反其说欤。其为图式信矣。世多以子居西上为嫌。然行低字少。有若居隅者然。岂可谓当尊者也。
主。反其说欤。其为图式信矣。世多以子居西上为嫌。然行低字少。有若居隅者然。岂可谓当尊者也。练服不言其制云云
陈练服下详说。为冠去首绖等事。则不可谓不言其制矣。其服则旧制有之。不须更言。世多以水浣旧服为练。非也。信斯言也。其所谓前期一日。陈练服者。何服也。厥明入哭。出就次易服。复入哭。何服也。其练之不以旧而以新。审矣。所谓练者。略熟疏淡。不至甚粗如初服也。此则文义甚明。非但鄙见如此。亦出于当时知道者之言。
大祥章下注。奉主遽迁。似皆俟禫毕袷祭后行之。今人权安别处。以待禫毕云云。
大祥章。奉神主入祠堂之仪。其下注则信然矣。然古者昭穆有序。各有其庙。故虽既祥而犹祔祖父之庙。其俟禫毕袷祭后行之。各安于孝子之心矣。今也群主一室。既无所袝之地。则必藏新主于别处。然后可以行古意云。是则得其半而失其半者也。盖灵筵既撤。神无所安顿。而别无异地。迟待禫毕之日。岂安于人情。以亲疏远近言之。孝子之不安其心。有甚于亡者待祖考之意。其轻重取舍。必有所在矣。况丧制节次。先后不紊。而其告迁奉入。既在于大祥之日。则其小注虽出于思古之意。而通行常礼。则不在彼而在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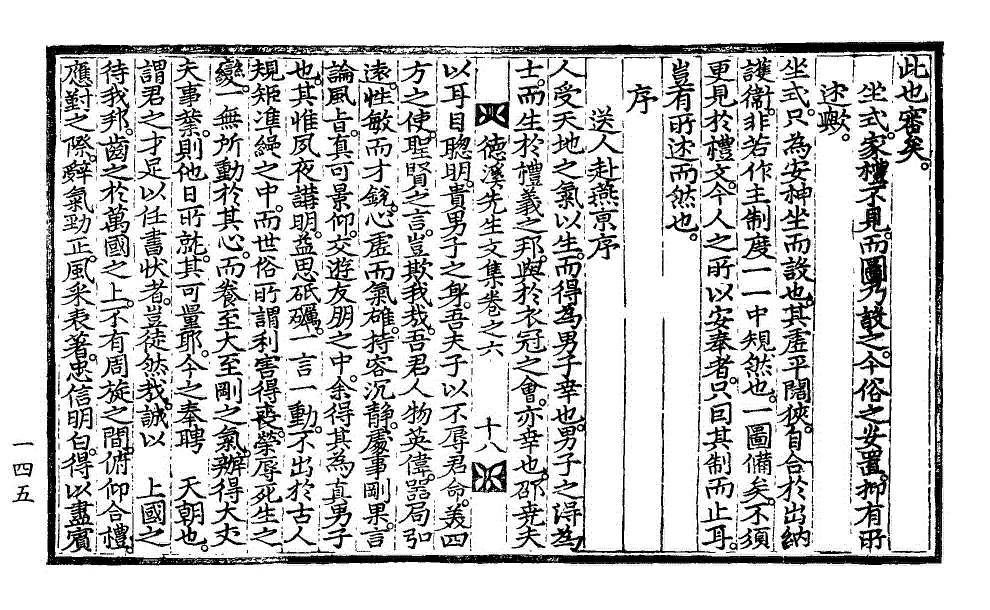 此也审矣。
此也审矣。坐式。家礼不见。而图乃设之。今俗之安置。抑有所述欤。
坐式。只为安神坐而设也。其虚平阔狭。自合于出纳护卫。非若作主制度一一中规然也。一图备矣。不须更见于礼文。今人之所以安奉者。只因其制而止耳。岂有所述而然也。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
送人赴燕京序[吴健]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得为男子幸也。男子之得为士。而生于礼义之邦。与于衣冠之会。亦幸也。邵尧夫以耳目聪明。贵男子之身。吾夫子以不辱君命。美四方之使。圣贤之言。岂欺我哉。吾君人物英伟。器局弘远。性敏而才锐。心虚而气雄。持容沈静。处事刚果。言论风旨。真可景仰。交游友朋之中。余得其为真男子也。其惟夙夜讲明。益思砥砺。一言一动。不出于古人规矩准绳之中。而世俗所谓利害得丧。荣辱死生之变。一无所动于其心。而养至大至刚之气。办得大丈夫事业。则他日所就。其可量耶。今之奉聘 天朝也。谓君之才足以任书状者。岂徒然哉。诚以 上国之待我邦。齿之于万国之上。不有周旋之间。俯仰合礼。应对之际。辞气劲正。风采表著。忠信明白。得以尽宾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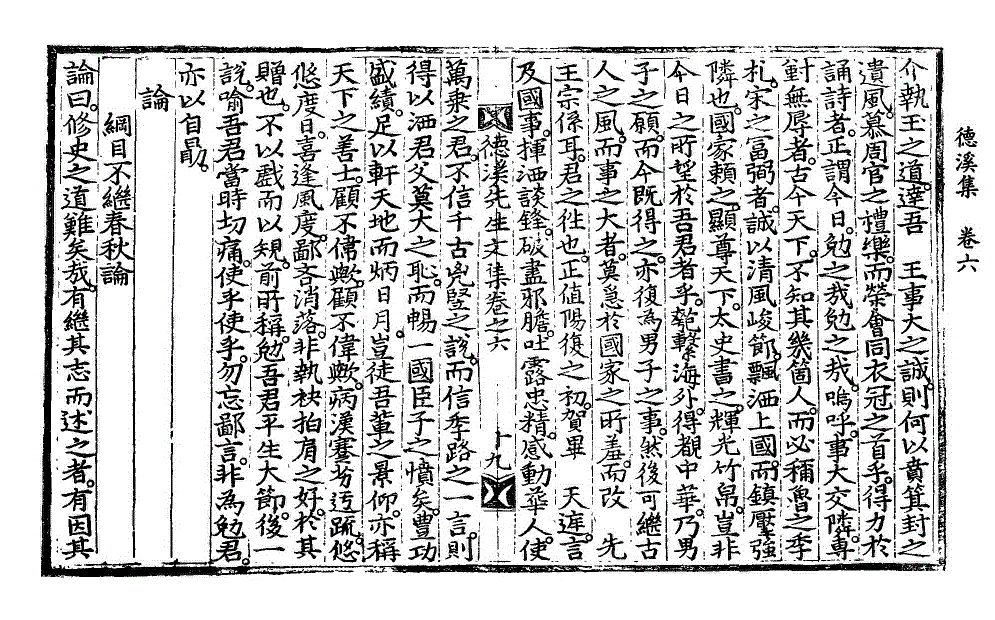 介执玉之道。达吾 王事大之诚。则何以贲箕封之遗风。慕周官之礼乐。而荣会同衣冠之首乎。得力于诵诗者。正谓今日。勉之哉勉之哉。呜呼。事大交邻。专对无辱者。古今天下。不知其几个人。而必称鲁之季札。宋之富弼者。诚以清风峻节。飘洒上国。而镇压强邻也。国家赖之。显尊天下。太史书之。辉光竹帛。岂非今日之所望于吾君者乎。匏系海外。得睹中华。乃男子之愿。而今既得之。亦复为男子之事。然后可继古人之风。而事之大者。莫急于国家之所羞。而改 先王宗系耳。君之往也。正值阳复之初。贺毕 天庭。言及国事。挥洒谈锋。破尽邪胆。吐露忠精。感动华人。使万乘之君。不信千古凶竖之说。而信季路之一言。则得以洒君父莫大之耻。而畅一国臣子之愤矣。礼功盛绩。足以轩天地而炳日月。岂徒吾辈之景仰。亦称天下之善士。顾不伟欤。顾不伟欤。病汉蹇劣迂疏。悠悠度日。喜逢风度。鄙吝消落。非执袂拍肩之好。于其赠也。不以戏而以规。前所称。勉吾君平生大节。后一说。喻吾君当时切痛。使乎使乎。勿忘鄙言。非为勉君。亦以自勖。
介执玉之道。达吾 王事大之诚。则何以贲箕封之遗风。慕周官之礼乐。而荣会同衣冠之首乎。得力于诵诗者。正谓今日。勉之哉勉之哉。呜呼。事大交邻。专对无辱者。古今天下。不知其几个人。而必称鲁之季札。宋之富弼者。诚以清风峻节。飘洒上国。而镇压强邻也。国家赖之。显尊天下。太史书之。辉光竹帛。岂非今日之所望于吾君者乎。匏系海外。得睹中华。乃男子之愿。而今既得之。亦复为男子之事。然后可继古人之风。而事之大者。莫急于国家之所羞。而改 先王宗系耳。君之往也。正值阳复之初。贺毕 天庭。言及国事。挥洒谈锋。破尽邪胆。吐露忠精。感动华人。使万乘之君。不信千古凶竖之说。而信季路之一言。则得以洒君父莫大之耻。而畅一国臣子之愤矣。礼功盛绩。足以轩天地而炳日月。岂徒吾辈之景仰。亦称天下之善士。顾不伟欤。顾不伟欤。病汉蹇劣迂疏。悠悠度日。喜逢风度。鄙吝消落。非执袂拍肩之好。于其赠也。不以戏而以规。前所称。勉吾君平生大节。后一说。喻吾君当时切痛。使乎使乎。勿忘鄙言。非为勉君。亦以自勖。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论
纲目不继春秋论
论曰。修史之道难矣哉。有继其志而述之者。有因其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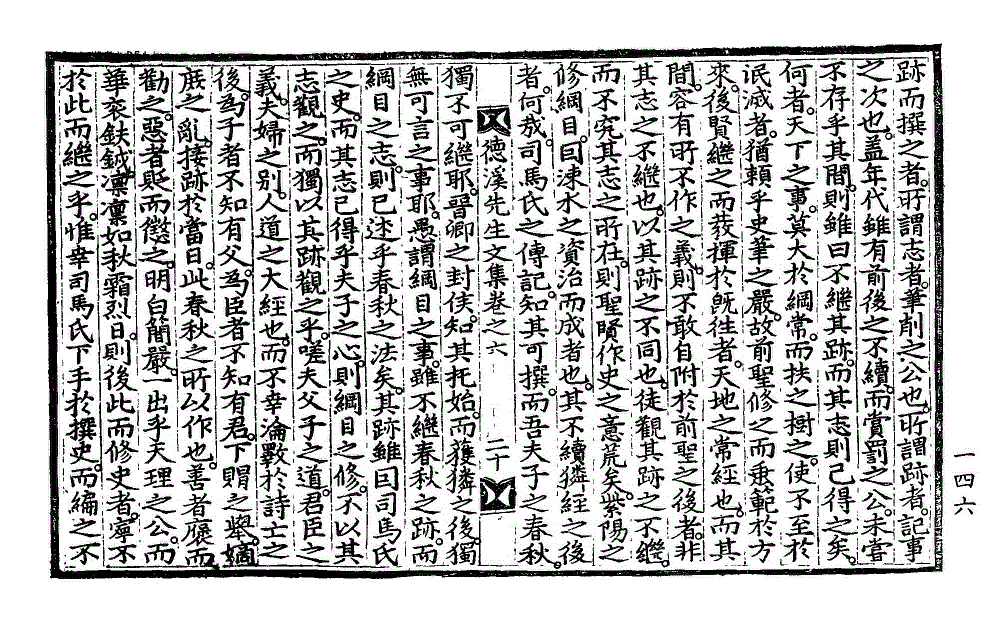 迹而撰之者。所谓志者。笔削之公也。所谓迹者。记事之次也。盖年代虽有前后之不续。而赏罚之公。未尝不存乎其间。则虽曰不继其迹。而其志则已得之矣。何者。天下之事。莫大于纲常。而扶之树之。使不至于泯灭者。犹赖乎史笔之严。故前圣修之而垂范于方来。后贤继之而发挥于既往者。天地之常经也。而其间。容有所不作之义。则不敢自附于前圣之后者。非其志之不继也。以其迹之不同也。徒观其迹之不继。而不究其志之所在。则圣贤作史之意荒矣。紫阳之修纲目。因涑水之资治而成者也。其不续獜经之后者。何哉。司马氏之传记。知其可撰。而吾夫子之春秋。独不可继耶。晋卿之封侯。知其托始。而获獜之后。独无可言之事耶。愚谓纲目之事。虽不继春秋之迹。而纲目之志。则已述乎春秋之法矣。其迹虽因司马氏之史。而其志已得乎夫子之心。则纲目之修。不以其志观之。而独以其迹观之乎。嗟夫父子之道。君臣之义。夫妇之别。人道之大经也。而不幸沦斁于诗亡之后。为子者不知有父。为臣者不知有君。下赗之举。嫡庶之乱。接迹于当日。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善者褒而劝之。恶者贬而惩之。明白简严。一出乎天理之公。而华衮鈇钺。凛凛如秋霜烈日。则后此而修史者。宁不于此而继之乎。惟幸司马氏下手于撰史。而编之不
迹而撰之者。所谓志者。笔削之公也。所谓迹者。记事之次也。盖年代虽有前后之不续。而赏罚之公。未尝不存乎其间。则虽曰不继其迹。而其志则已得之矣。何者。天下之事。莫大于纲常。而扶之树之。使不至于泯灭者。犹赖乎史笔之严。故前圣修之而垂范于方来。后贤继之而发挥于既往者。天地之常经也。而其间。容有所不作之义。则不敢自附于前圣之后者。非其志之不继也。以其迹之不同也。徒观其迹之不继。而不究其志之所在。则圣贤作史之意荒矣。紫阳之修纲目。因涑水之资治而成者也。其不续獜经之后者。何哉。司马氏之传记。知其可撰。而吾夫子之春秋。独不可继耶。晋卿之封侯。知其托始。而获獜之后。独无可言之事耶。愚谓纲目之事。虽不继春秋之迹。而纲目之志。则已述乎春秋之法矣。其迹虽因司马氏之史。而其志已得乎夫子之心。则纲目之修。不以其志观之。而独以其迹观之乎。嗟夫父子之道。君臣之义。夫妇之别。人道之大经也。而不幸沦斁于诗亡之后。为子者不知有父。为臣者不知有君。下赗之举。嫡庶之乱。接迹于当日。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善者褒而劝之。恶者贬而惩之。明白简严。一出乎天理之公。而华衮鈇钺。凛凛如秋霜烈日。则后此而修史者。宁不于此而继之乎。惟幸司马氏下手于撰史。而编之不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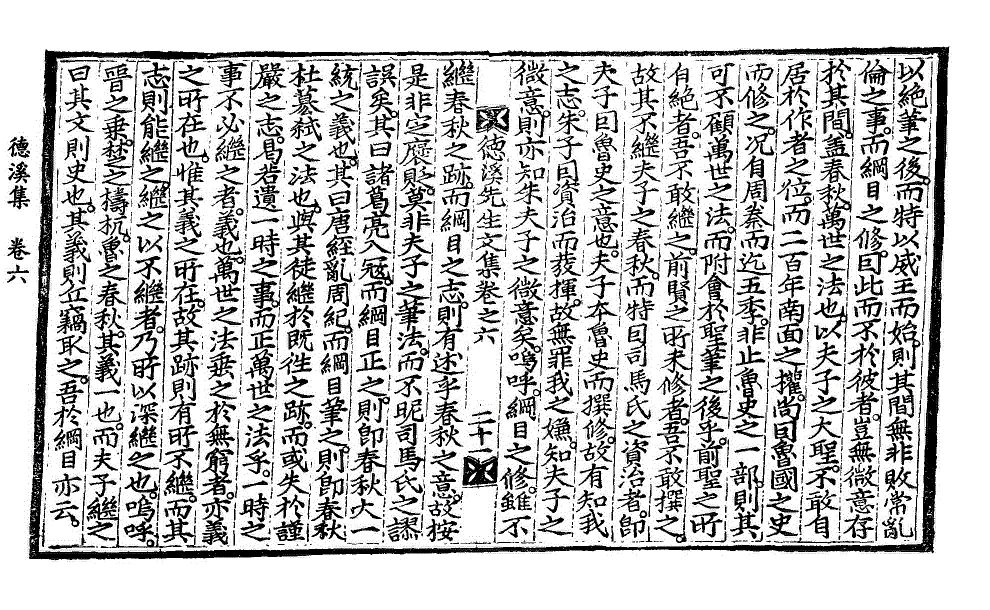 以绝笔之后。而特以威王而始。则其间无非败常乱伦之事。而纲目之修。因比而不于彼者。岂无微意存于其间。盖春秋。万世之法也。以夫子之大圣。不敢自居于作者之位。而二百年南面之权。尚因鲁国之史而修之。况自周秦而迄五季。非止鲁史之一部。则其可不顾万世之法。而附会于圣笔之后乎。前圣之所自绝者。吾不敢继之。前贤之所未修者。吾不敢撰之。故其不继夫子之春秋。而特因司马氏之资治者。即夫子因鲁史之意也。夫子本鲁史而撰修。故有知我之志。朱子因资治而发挥。故无罪我之嫌。知夫子之微意。则亦知朱夫子之微意矣。呜呼。纲目之修。虽不继春秋之迹。而纲目之志。则有述乎春秋之意。故按是非定褒贬。莫非夫子之笔法。而不昵司马氏之谬误矣。其曰诸葛亮入寇。而纲目正之。则即春秋大一统之义也。其曰唐经乱周纪。而纲目笔之。则即春秋杜篡弑之法也。与其徒继于既往之迹。而或失于谨严之志。曷若遗一时之事。而正万世之法乎。一时之事不必继之者。义也。万世之法垂之于无穷者。亦义之所在也。惟其义之所在。故其迹则有所不继。而其志则能继之。继之以不继者。乃所以深继之也。呜呼。晋之乘。楚之梼杭。鲁之春秋。其义一也。而夫子继之曰其文则史也。其义则丘窃取之。吾于纲目亦云。
以绝笔之后。而特以威王而始。则其间无非败常乱伦之事。而纲目之修。因比而不于彼者。岂无微意存于其间。盖春秋。万世之法也。以夫子之大圣。不敢自居于作者之位。而二百年南面之权。尚因鲁国之史而修之。况自周秦而迄五季。非止鲁史之一部。则其可不顾万世之法。而附会于圣笔之后乎。前圣之所自绝者。吾不敢继之。前贤之所未修者。吾不敢撰之。故其不继夫子之春秋。而特因司马氏之资治者。即夫子因鲁史之意也。夫子本鲁史而撰修。故有知我之志。朱子因资治而发挥。故无罪我之嫌。知夫子之微意。则亦知朱夫子之微意矣。呜呼。纲目之修。虽不继春秋之迹。而纲目之志。则有述乎春秋之意。故按是非定褒贬。莫非夫子之笔法。而不昵司马氏之谬误矣。其曰诸葛亮入寇。而纲目正之。则即春秋大一统之义也。其曰唐经乱周纪。而纲目笔之。则即春秋杜篡弑之法也。与其徒继于既往之迹。而或失于谨严之志。曷若遗一时之事。而正万世之法乎。一时之事不必继之者。义也。万世之法垂之于无穷者。亦义之所在也。惟其义之所在。故其迹则有所不继。而其志则能继之。继之以不继者。乃所以深继之也。呜呼。晋之乘。楚之梼杭。鲁之春秋。其义一也。而夫子继之曰其文则史也。其义则丘窃取之。吾于纲目亦云。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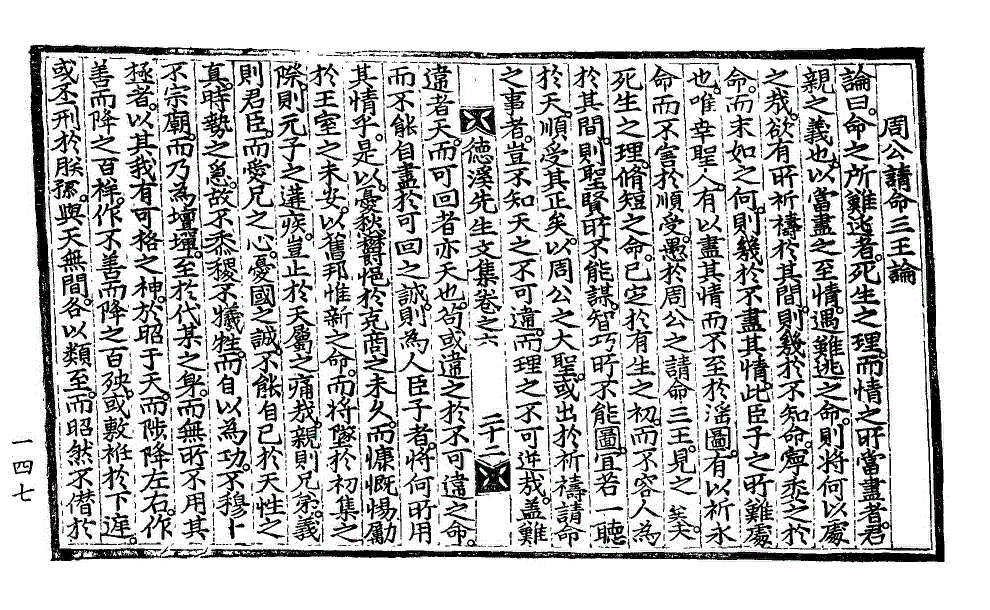 周公请命三王论
周公请命三王论论曰。命之所难逃者。死生之理。而情之所当尽者。君亲之义也。以当尽之至情。遇难逃之命。则将何以处之哉。欲有所祈祷于其间。则几于不知命。宁委之于命。而末如之何。则几于不尽其情。此臣子之所难处也。唯幸圣人。有以尽其情而不至于淫图。有以祈永命而不害于顺受。愚于周公之请命三王。见之矣。夫死生之理。脩短之命。已定于有生之初。而不容人为于其间。则圣贤所不能谋。智巧所不能图。宜若一听于天。顺受其正矣。以周公之大圣。或出于祈祷请命之事者。岂不知天之不可违。而理之不可逆哉。盖难违者天。而可回者亦天也。苟或违之于不可违之命。而不能自尽于可回之诚。则为人臣子者。将何所用其情乎。是以。忧愁郁悒于克商之未久。而慷慨惕励于王室之未安。以旧邦惟新之命。而将坠于初集之际。则元子之遘疾。岂止于天属之痛哉。亲则兄弟。义则君臣。而爱兄之心。忧国之诚。不能自已于天性之真。时势之急。故不黍稷不牺牲。而自以为功。不穆卜不宗庙。而乃为坛墠。至于代某之身。而无所不用其极者。以其我有可格之神。于昭于天。而陟降左右。作善而降之百祥。作不善而降之百殃。或敷衽于下庭。或丕刑于朕孙。与天无间。各以类至。而昭然不僣于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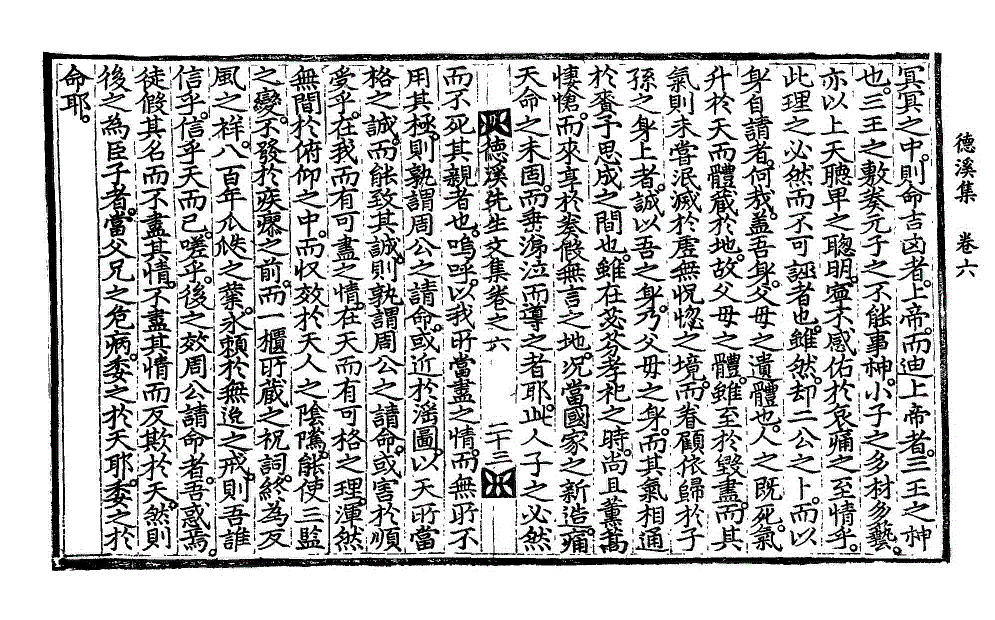 冥冥之中。则命吉凶者。上帝。而迪上帝者。三王之神也。三王之敷奏元子之不能事神。小子之多材多艺。亦以上天听卑之聪明。宁不感佑于哀痛之至情乎。此理之必然而不可诬者也。虽然。却二公之卜。而以身自请者。何哉。盖吾身。父母之遗体也。人之既死。气升于天而体藏于地。故父母之体。虽至于毁尽。而其气则未尝泯灭于虚无恍惚之境。而眷顾依归于子孙之身上者。诚以吾之身。乃父母之身。而其气相通于赉子思成之间也。虽在苾芬孝祀之时。尚且薰蒿悽怆。而来享于奏假无言之地。况当国家之新造。痛天命之未固。而垂涕泣而导之者耶。此人子之必然而不死其亲者也。呜呼。以我所当尽之情。而无所不用其极。则孰谓周公之请命。或近于淫图。以天所当格之诚。而能致其诚。则孰谓周公之请命。或害于顺受乎。在我而有可尽之情。在天而有可格之理。浑然无间于俯仰之中。而收效于天人之阴骘。能使三监之变。不发于疾瘳之前。而一匮所藏之祝词。终为反风之祥。八百年瓜瓞之业。永赖于无逸之戒。则吾谁信乎。信乎天而已。嗟乎。后之效周公请命者。吾惑焉。徒假其名而不尽其情。不尽其情而反欺于天。然则后之为臣子者。当父兄之危病。委之于天耶。委之于命耶。
冥冥之中。则命吉凶者。上帝。而迪上帝者。三王之神也。三王之敷奏元子之不能事神。小子之多材多艺。亦以上天听卑之聪明。宁不感佑于哀痛之至情乎。此理之必然而不可诬者也。虽然。却二公之卜。而以身自请者。何哉。盖吾身。父母之遗体也。人之既死。气升于天而体藏于地。故父母之体。虽至于毁尽。而其气则未尝泯灭于虚无恍惚之境。而眷顾依归于子孙之身上者。诚以吾之身。乃父母之身。而其气相通于赉子思成之间也。虽在苾芬孝祀之时。尚且薰蒿悽怆。而来享于奏假无言之地。况当国家之新造。痛天命之未固。而垂涕泣而导之者耶。此人子之必然而不死其亲者也。呜呼。以我所当尽之情。而无所不用其极。则孰谓周公之请命。或近于淫图。以天所当格之诚。而能致其诚。则孰谓周公之请命。或害于顺受乎。在我而有可尽之情。在天而有可格之理。浑然无间于俯仰之中。而收效于天人之阴骘。能使三监之变。不发于疾瘳之前。而一匮所藏之祝词。终为反风之祥。八百年瓜瓞之业。永赖于无逸之戒。则吾谁信乎。信乎天而已。嗟乎。后之效周公请命者。吾惑焉。徒假其名而不尽其情。不尽其情而反欺于天。然则后之为臣子者。当父兄之危病。委之于天耶。委之于命耶。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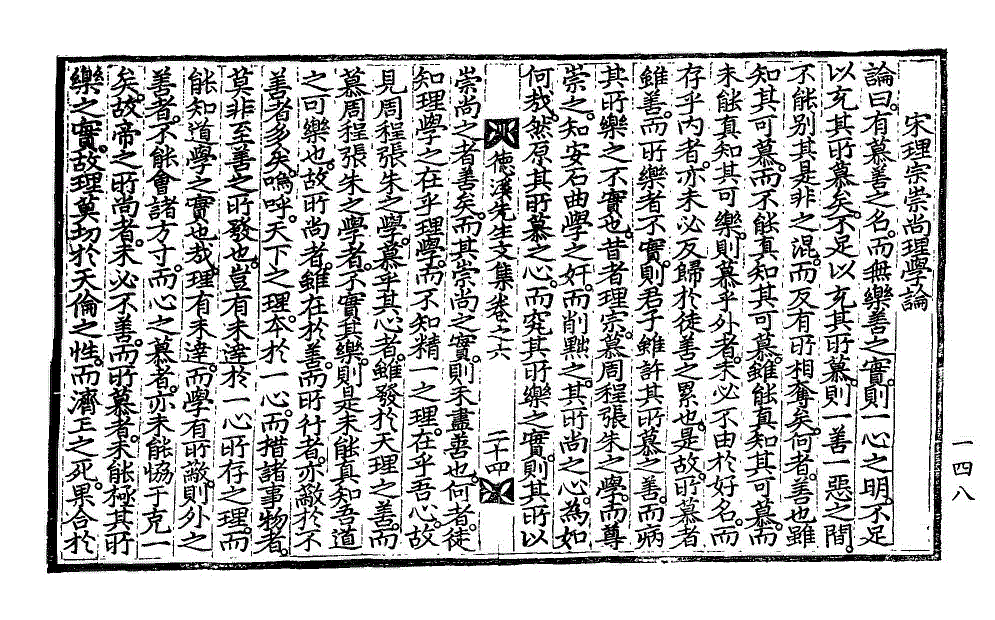 宋理宗崇尚理学论
宋理宗崇尚理学论论曰。有慕善之名。而无乐善之实。则一心之明。不足以充其所慕矣。不足以充其所慕。则一善一恶之间。不能别其是非之混。而反有所相夺矣。何者。善也虽知其可慕。而不能真知其可慕。虽能真知其可慕。而未能真知其可乐。则慕乎外者。未必不由于好名。而存乎内者。亦未必反归于徒善之累也。是故。所慕者虽善。而所乐者不实。则君子虽许其所慕之善。而病其所乐之不实也。昔者理宗。慕周程张朱之学。而尊崇之。知安石曲学之奸。而削黜之。其所尚之心。为如何哉。然原其所慕之心。而究其所乐之实。则其所以崇尚之者善矣。而其崇尚之实。则未尽善也。何者。徒知理学之在乎理学。而不知精一之理。在乎吾心。故见周程张朱之学。慕乎其心者。虽发于天理之善。而慕周程张朱之学者。不实其乐。则是未能真知吾道之可乐也。故所尚者。虽在于善。而所行者。亦蔽于不善者多矣。呜呼。天下之理。本于一心。而措诸事物者。莫非至善之所发也。岂有未达于一心所存之理。而能知道学之实也哉。理有未达。而学有所蔽。则外之善者。不能会诸方寸。而心之慕者。亦未能协于克一矣。故帝之所尚者。未必不善。而所慕者。未能极其所乐之实。故理莫切于天伦之性。而济王之死。果合于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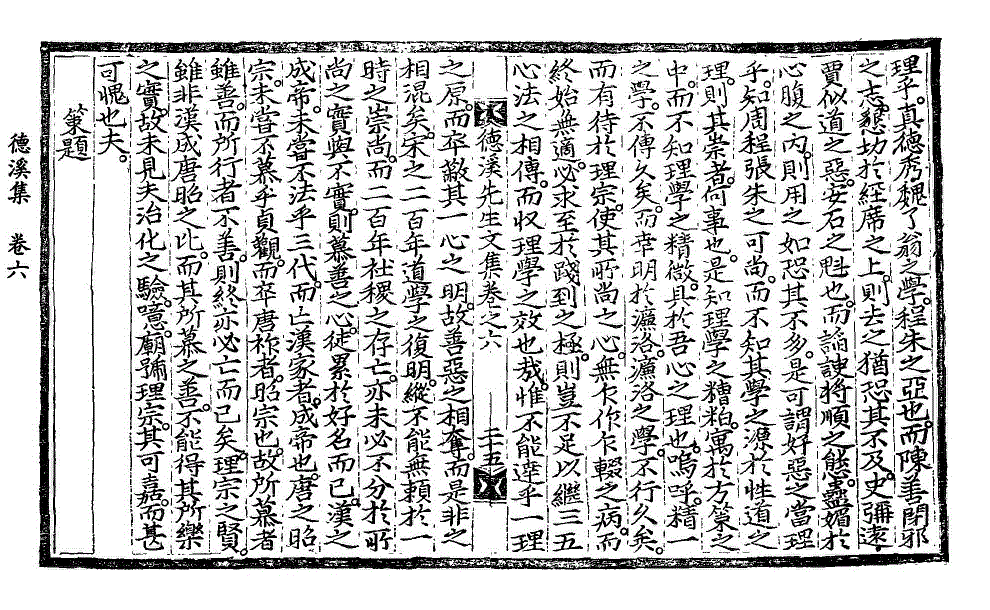 理乎。真德秀,魏了翁之学。程朱之亚也。而陈善闭邪之志。恳切于经席之上。则去之犹恐其不及。史弥远,贾似道之恶。安石之魁也。而謟谀将顺之态。蛊媚于心腹之内。则用之如恐其不多。是可谓好恶之当理乎。知周程张朱之可尚。而不知其学之源于性道之理。则其崇者。何事也。是知理学之糟粕。寓于方策之中。而不知理学之精微。具于吾心之理也。呜呼。精一之学。不传久矣。而幸明于濂洛。濂洛之学。不行久矣。而有待于理宗。使其所尚之心。无乍作乍辍之病。而终始无适。必求至于践到之极。则岂不足以继三五心法之相传。而收理学之效也哉。惟不能达乎一理之原。而卒蔽其一心之明。故善恶之相夺。而是非之相混矣。宋之二百年道学之复明。纵不能无赖于一时之崇尚。而二百年社稷之存亡。亦未必不分于所尚之实与不实。则慕善之心。徒累于好名而已。汉之成帝。未尝不法乎三代。而亡汉家者。成帝也。唐之昭宗。未尝不慕乎贞观。而卒唐祚者。昭宗也。故所慕者虽善。而所行者不善。则终亦必亡而已矣。理宗之贤。虽非汉成唐昭之比。而其所慕之善。不能得其所乐之实。故未见夫治化之验。噫。庙号理宗。其可嘉。而甚可愧也夫。
理乎。真德秀,魏了翁之学。程朱之亚也。而陈善闭邪之志。恳切于经席之上。则去之犹恐其不及。史弥远,贾似道之恶。安石之魁也。而謟谀将顺之态。蛊媚于心腹之内。则用之如恐其不多。是可谓好恶之当理乎。知周程张朱之可尚。而不知其学之源于性道之理。则其崇者。何事也。是知理学之糟粕。寓于方策之中。而不知理学之精微。具于吾心之理也。呜呼。精一之学。不传久矣。而幸明于濂洛。濂洛之学。不行久矣。而有待于理宗。使其所尚之心。无乍作乍辍之病。而终始无适。必求至于践到之极。则岂不足以继三五心法之相传。而收理学之效也哉。惟不能达乎一理之原。而卒蔽其一心之明。故善恶之相夺。而是非之相混矣。宋之二百年道学之复明。纵不能无赖于一时之崇尚。而二百年社稷之存亡。亦未必不分于所尚之实与不实。则慕善之心。徒累于好名而已。汉之成帝。未尝不法乎三代。而亡汉家者。成帝也。唐之昭宗。未尝不慕乎贞观。而卒唐祚者。昭宗也。故所慕者虽善。而所行者不善。则终亦必亡而已矣。理宗之贤。虽非汉成唐昭之比。而其所慕之善。不能得其所乐之实。故未见夫治化之验。噫。庙号理宗。其可嘉。而甚可愧也夫。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策题
[为学之道]
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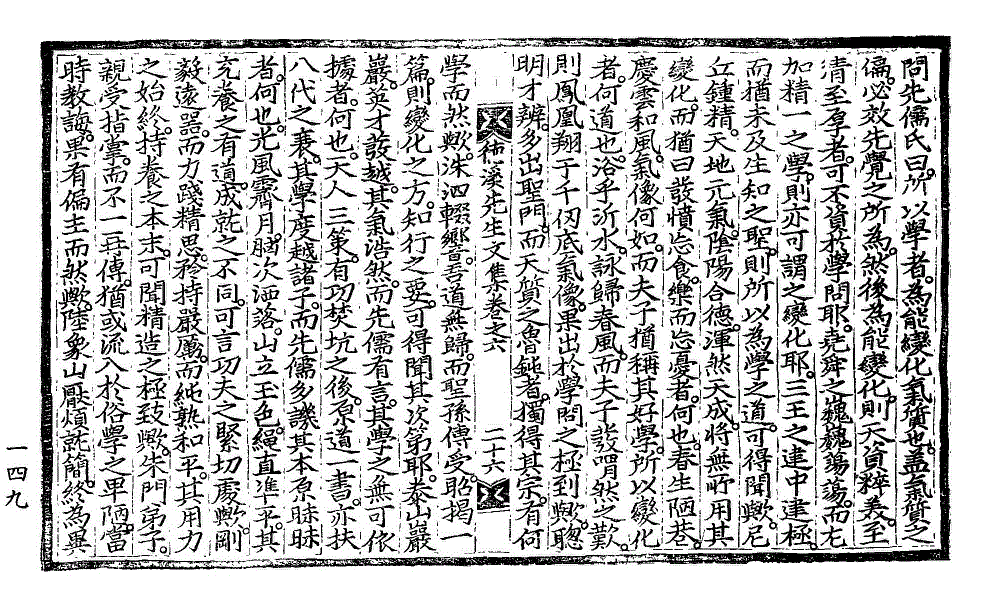 问先儒氏曰。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也。盖气质之偏。必效先觉之所为。然后为能变化。则天资粹美。至清至厚者。可不资于学问耶。尧舜之巍巍荡荡。而尤加精一之学。则亦可谓之变化耶。三王之建中建极。而犹未及生知之圣。则所以为学之道。可得闻欤。尼丘钟精。天地元气。阴阳合德。浑然天成。将无所用其变化。而犹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者。何也。春生陋巷。庆云和风。气像何如。而夫子犹称其好学。所以变化者。何道也。浴乎沂水。咏归春风。而夫子发喟然之叹。则凤凰翔于千仞底气像。果出于学问之极到欤。聪明才辨。多出圣门。而天质之鲁钝者。独得其宗。有何学而然欤。洙泗辍响。吾道无归。而圣孙传受。昭揭一篇。则变化之方。知行之要。可得闻其次第耶。泰山岩岩。英才发越。其气浩然。而先儒有言。其学之无可依据者。何也。天人三策。有功焚坑之后。原道一书。亦扶八代之衰。其学度越诸子。而先儒多讥其本原昧昧者。何也。光风霁月。胸次洒落。山立玉色。绳直准平。其充养之有道。成就之不同。可言功夫之紧切处欤。刚毅远器。而力践精思。矜持严厉。而纯熟和平。其用力之始终。持养之本末。可闻精造之极致欤。朱门弟子。亲受指掌。而不一再传。犹或流入于俗学之卑陋。当时教诲。果有偏主而然欤。陆象山厌烦就简。终为异
问先儒氏曰。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也。盖气质之偏。必效先觉之所为。然后为能变化。则天资粹美。至清至厚者。可不资于学问耶。尧舜之巍巍荡荡。而尤加精一之学。则亦可谓之变化耶。三王之建中建极。而犹未及生知之圣。则所以为学之道。可得闻欤。尼丘钟精。天地元气。阴阳合德。浑然天成。将无所用其变化。而犹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者。何也。春生陋巷。庆云和风。气像何如。而夫子犹称其好学。所以变化者。何道也。浴乎沂水。咏归春风。而夫子发喟然之叹。则凤凰翔于千仞底气像。果出于学问之极到欤。聪明才辨。多出圣门。而天质之鲁钝者。独得其宗。有何学而然欤。洙泗辍响。吾道无归。而圣孙传受。昭揭一篇。则变化之方。知行之要。可得闻其次第耶。泰山岩岩。英才发越。其气浩然。而先儒有言。其学之无可依据者。何也。天人三策。有功焚坑之后。原道一书。亦扶八代之衰。其学度越诸子。而先儒多讥其本原昧昧者。何也。光风霁月。胸次洒落。山立玉色。绳直准平。其充养之有道。成就之不同。可言功夫之紧切处欤。刚毅远器。而力践精思。矜持严厉。而纯熟和平。其用力之始终。持养之本末。可闻精造之极致欤。朱门弟子。亲受指掌。而不一再传。犹或流入于俗学之卑陋。当时教诲。果有偏主而然欤。陆象山厌烦就简。终为异德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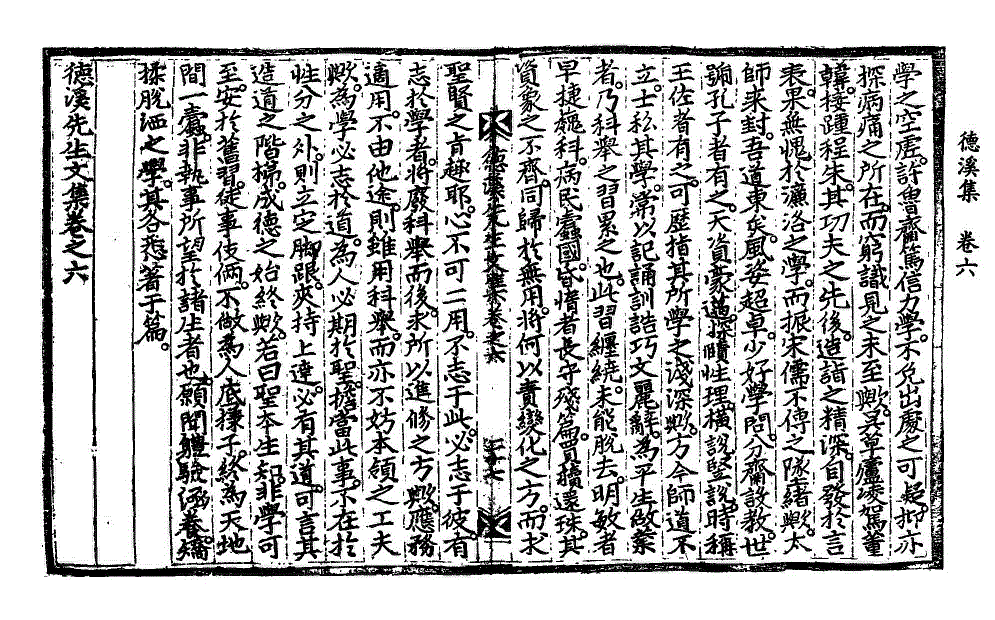 学之空虚。许鲁斋惊信力学。不免出处之可疑。抑亦探病痛之所在。而穷识见之未至欤。吴草庐凌驾董韩。接踵程朱。其功夫之先后。造诣之精深。自发于言表。果无愧于濂洛之学。而振宋儒不传之坠绪欤。太师来封。吾道东矣。风姿超卓。少好学问。分斋设教。世号孔子者有之。天资豪迈。探赜性理。横说竖说。时称王佐者有之。可历指其所学之浅深欤。方今师道不立。士私其学。常以记诵训诰巧文丽辞。为平生做业者。乃科举之习累之也。此习缠绕。未能脱去。明敏者早捷巍科。病民蠹国。昏惰者长守残篇。买椟还珠。其资象之不齐。同归于无用。将何以责变化之方。而求圣贤之旨趣耶。心不可二用。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有志于学者。将废科举而后。求所以进修之方欤。应务适用。不由他途。则虽用科举。而亦不妨本领之工夫欤。为学必志于道。为人必期于圣。担当此事。不在于性分之外。则立定脚跟。夹持上达。必有其道。可言其造道之阶梯。成德之始终欤。若曰圣本生知。非学可至。安于旧习。徒事伎俩。不做为人底样子。终为天地间一蠹。非执事所望于诸生者也。愿闻体验涵养。矫揉脱洒之学。其各悉著于篇。
学之空虚。许鲁斋惊信力学。不免出处之可疑。抑亦探病痛之所在。而穷识见之未至欤。吴草庐凌驾董韩。接踵程朱。其功夫之先后。造诣之精深。自发于言表。果无愧于濂洛之学。而振宋儒不传之坠绪欤。太师来封。吾道东矣。风姿超卓。少好学问。分斋设教。世号孔子者有之。天资豪迈。探赜性理。横说竖说。时称王佐者有之。可历指其所学之浅深欤。方今师道不立。士私其学。常以记诵训诰巧文丽辞。为平生做业者。乃科举之习累之也。此习缠绕。未能脱去。明敏者早捷巍科。病民蠹国。昏惰者长守残篇。买椟还珠。其资象之不齐。同归于无用。将何以责变化之方。而求圣贤之旨趣耶。心不可二用。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有志于学者。将废科举而后。求所以进修之方欤。应务适用。不由他途。则虽用科举。而亦不妨本领之工夫欤。为学必志于道。为人必期于圣。担当此事。不在于性分之外。则立定脚跟。夹持上达。必有其道。可言其造道之阶梯。成德之始终欤。若曰圣本生知。非学可至。安于旧习。徒事伎俩。不做为人底样子。终为天地间一蠹。非执事所望于诸生者也。愿闻体验涵养。矫揉脱洒之学。其各悉著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