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书
书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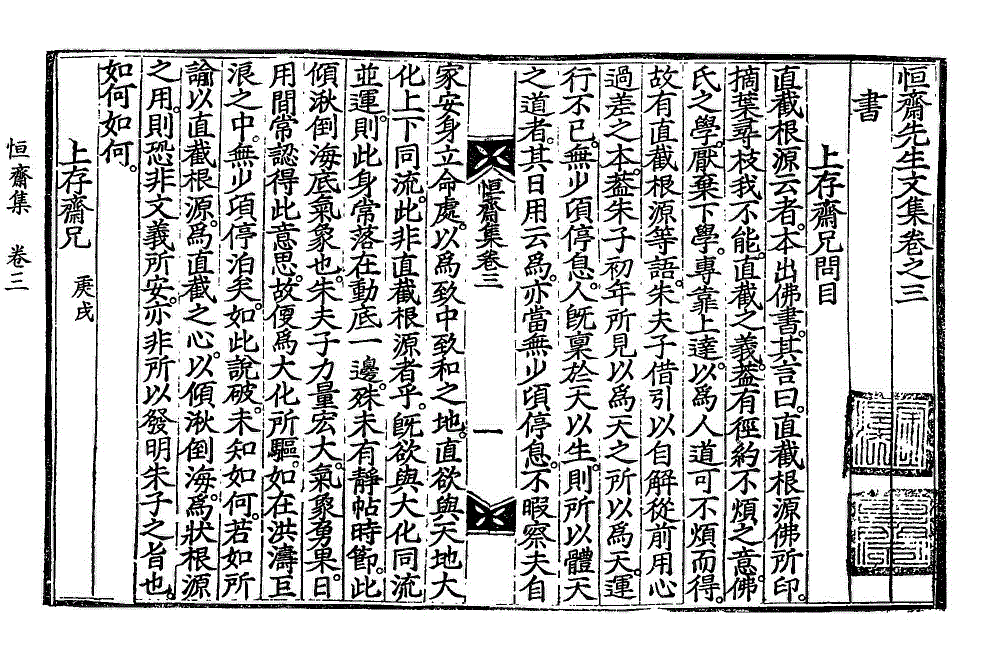 上存斋兄问目
上存斋兄问目直截根源云者。本出佛书。其言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直截之义。盖有径约不烦之意。佛氏之学。厌弃下学。专靠上达。以为人道可不烦而得。故有直截根源等语。朱夫子借引以自解从前用心过差之本。盖朱子初年所见以为天之所以为天。运行不已。无少顷停息。人既禀于天以生。则所以体天之道者。其日用云为。亦当无少顷停息。不暇察夫自家安身立命处。以为致中致和之地。直欲与天地大化上下同流。此非直截根源者乎。既欲与大化同流并运。则此身常落在动底一边。殊未有静帖时节。此倾湫倒海底气象也。朱夫子力量宏大。气象勇果。日用间常认得此意思。故便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无少顷停泊矣。如此说破。未知如何。若如所谕以直截根源。为直截之心。以倾湫倒海。为状根源之用。则恐非文义所安。亦非所以发明朱子之旨也。如何如何。
上存斋兄(庚戌)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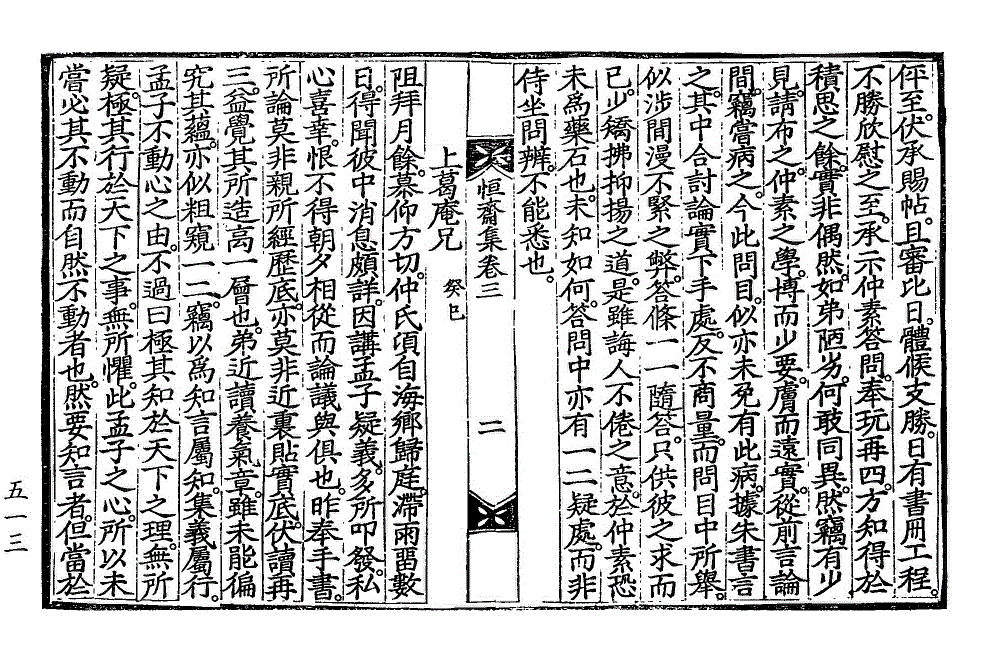 伻至。伏承赐帖。且审比日。体候支胜。日有书册工程。不胜欣慰之至。承示仲素答问。奉玩再四。方知得于积思之馀。实非偶然。如弟陋劣。何敢同异。然窃有少见。请布之。仲素之学。博而少要。肤而远实。从前言论间。窃尝病之。今此问目。似亦未免有此病。据朱书言之。其中合讨论实下手处。反不商量。而问目中所举。似涉间漫不紧之弊。答条一一随答。只供彼之求而已。少矫拂抑剔之道。是虽诲人不倦之意。于仲素恐未为药石也。未知如何。答问中亦有一二疑处。而非侍坐问辨。不能悉也。
伻至。伏承赐帖。且审比日。体候支胜。日有书册工程。不胜欣慰之至。承示仲素答问。奉玩再四。方知得于积思之馀。实非偶然。如弟陋劣。何敢同异。然窃有少见。请布之。仲素之学。博而少要。肤而远实。从前言论间。窃尝病之。今此问目。似亦未免有此病。据朱书言之。其中合讨论实下手处。反不商量。而问目中所举。似涉间漫不紧之弊。答条一一随答。只供彼之求而已。少矫拂抑剔之道。是虽诲人不倦之意。于仲素恐未为药石也。未知如何。答问中亦有一二疑处。而非侍坐问辨。不能悉也。上葛庵兄(癸巳)
阻拜月馀。慕仰方切。仲氏顷自海乡归庭。滞雨留数日。得闻彼中消息颇详。因讲孟子疑义。多所叩发。私心喜幸。恨不得朝夕相从而论议与俱也。昨奉手书。所论莫非亲所经历底。亦莫非近里贴实底。伏读再三。益觉其所造高一层也。弟近读养气章。虽未能遍究其蕴。亦似粗窥一二。窃以为知言属知。集义属行。孟子不动心之由。不过曰极其知于天下之理。无所疑。极其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孟子之心。所以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者也。然要知言者。但当于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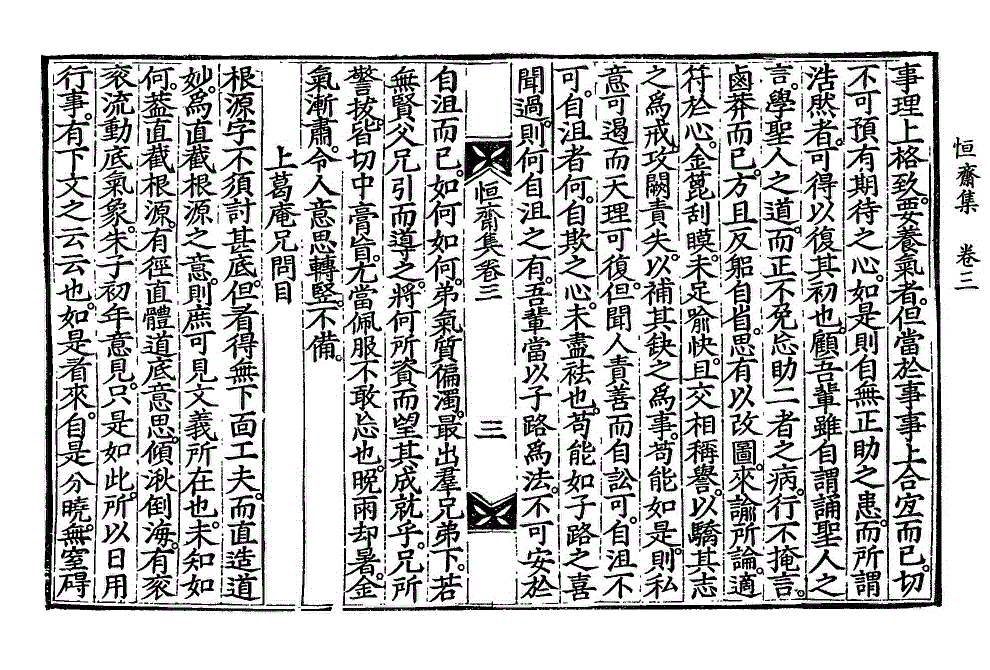 事理上格致。要养气者。但当于事事上合宜而已。切不可预有期待之心。如是则自无正助之患。而所谓浩然者。可得以复其初也。顾吾辈虽自谓诵圣人之言。学圣人之道。而正不免忘助二者之病。行不掩言。卤莽而已。方且反躬自省。思有以改图。来谕所论。适符于心。金篦刮瞙。未足喻快。且交相称誉。以骄其志之为戒。攻阙责失。以补其缺之为事。苟能如是。则私意可遏而天理可复。但闻人责善而自讼可。自沮不可。自沮者何。自欺之心。夫尽祛也。苟能如子路之喜闻过。则何自沮之有。吾辈当以子路为法。不可安于自沮而已。如何如何。弟气质偏浊。最出群兄弟下。若无贤父兄引而导之。将何所资而望其成就乎。兄所警拔。皆切中膏盲。尤当佩服不敢忘也。晚雨却暑。金气渐肃。令人意思转竖。不备。
事理上格致。要养气者。但当于事事上合宜而已。切不可预有期待之心。如是则自无正助之患。而所谓浩然者。可得以复其初也。顾吾辈虽自谓诵圣人之言。学圣人之道。而正不免忘助二者之病。行不掩言。卤莽而已。方且反躬自省。思有以改图。来谕所论。适符于心。金篦刮瞙。未足喻快。且交相称誉。以骄其志之为戒。攻阙责失。以补其缺之为事。苟能如是。则私意可遏而天理可复。但闻人责善而自讼可。自沮不可。自沮者何。自欺之心。夫尽祛也。苟能如子路之喜闻过。则何自沮之有。吾辈当以子路为法。不可安于自沮而已。如何如何。弟气质偏浊。最出群兄弟下。若无贤父兄引而导之。将何所资而望其成就乎。兄所警拔。皆切中膏盲。尤当佩服不敢忘也。晚雨却暑。金气渐肃。令人意思转竖。不备。上葛庵兄问目
根源字不须讨甚底。但看得无下面工夫。而直造道妙。为直截根源之意。则庶可见文义所在也。夫知如何。盖直截根源。有径直体道底意思。倾湫倒海。有衮衮流动底气象。朱子初年意见。只是如此。所以日用行事。有下文之云云也。如是看来。自是分晓。无窒碍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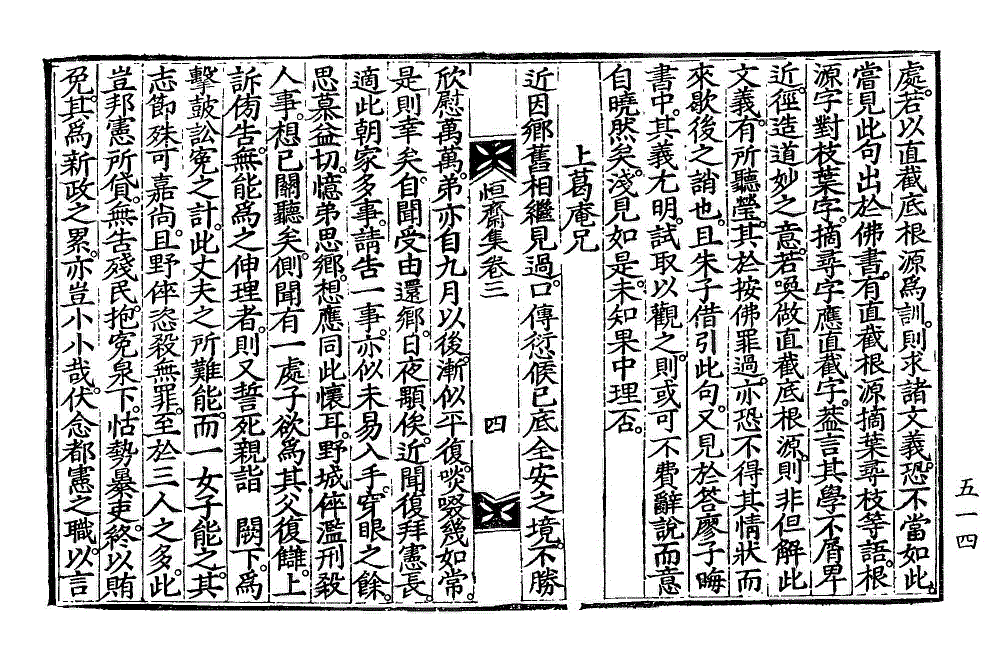 处。若以直截底根源为训。则求诸文义。恐不当如此。尝见此句出于佛书。有直截根源摘叶寻枝等语。根源字对枝叶字。摘寻字应直截字。盖言其学不屑卑近。径造道妙之意。若唤做直截底根源。则非但解此文义。有所听莹。其于按佛罪过。亦恐不得其情状而来歇后之诮也。且朱子借引此句。又见于答廖子晦书中。其义尤明。试取以观之。则或可不费辞说而意自晓然矣。浅见如是。未知果中理否。
处。若以直截底根源为训。则求诸文义。恐不当如此。尝见此句出于佛书。有直截根源摘叶寻枝等语。根源字对枝叶字。摘寻字应直截字。盖言其学不屑卑近。径造道妙之意。若唤做直截底根源。则非但解此文义。有所听莹。其于按佛罪过。亦恐不得其情状而来歇后之诮也。且朱子借引此句。又见于答廖子晦书中。其义尤明。试取以观之。则或可不费辞说而意自晓然矣。浅见如是。未知果中理否。上葛庵兄
近因乡旧相继见过。口传愆候已底全安之境。不胜欣慰万万。弟亦自九月以后。渐似平复。啖啜几如常。是则幸矣。自闻受由还乡。日夜颙俟。近闻复拜宪长。适此朝家多事。请告一事。亦似未易入手。穿眼之馀。思慕益切。忆弟思乡。想应同此怀耳。野城倅滥刑杀人事。想已关听矣。侧闻有一处子欲为其父复雠。上诉傍告。无能为之伸理者。则又誓死亲诣 阙下。为击鼓讼冤之计。此丈夫之所难能。而一女子能之。其志节殊可嘉尚。且野倅恣杀无罪。至于三人之多。此岂邦宪所贷。无告残民。抱冤泉下。怙势暴吏。终以贿免。其为新政之累。亦岂小小哉。伏念都宪之职。以言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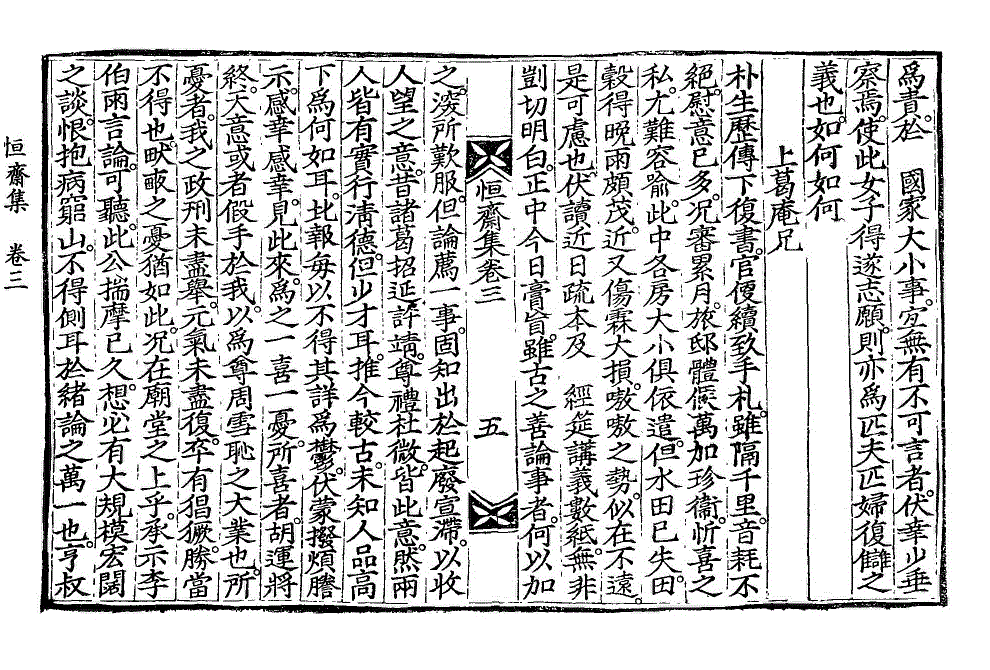 为责。于 国家大小事。宜无有不可言者。伏幸少垂察焉。使此女子得遂志愿。则亦为匹夫匹妇复雠之义也。如何如何。
为责。于 国家大小事。宜无有不可言者。伏幸少垂察焉。使此女子得遂志愿。则亦为匹夫匹妇复雠之义也。如何如何。上葛庵兄
朴生历传下复书。官便续致手札。虽隔千里。音耗不绝。慰意已多。况审累月。旅邸体侯万加珍卫。忻喜之私。尤难容喻。此中各房大小俱依遣。但水田已失。田谷得晚雨颇茂。近又伤霖大损。嗷嗷之势。似在不远。是可虑也。伏读近日疏本及 经筵讲义数纸。无非剀切明白。正中今日膏肓。虽古之善论事者。何以加之。深所叹服。但论荐一事。固知出于起废宣滞。以收人望之意。昔诸葛招延许靖。尊礼杜微。皆此意。然两人皆有实行清德。但少才耳。推今较古。未知人品高下为何如耳。北报每以不得其详为郁。伏蒙拨烦誊示。感幸感幸。见此来。为之一喜一忧。所喜者。胡运将终。天意或者假手于我。以为尊周雪耻之大业也。所忧者。我之政刑未尽举。元气未尽复。卒有猖獗。胜当不得也。畎亩之忧犹如此。况在庙堂之上乎。承示李伯雨言论。可听。此公揣摩已久。想必有大规模宏阔之谈。恨抱病穷山。不得侧耳于绪论之万一也。亨叔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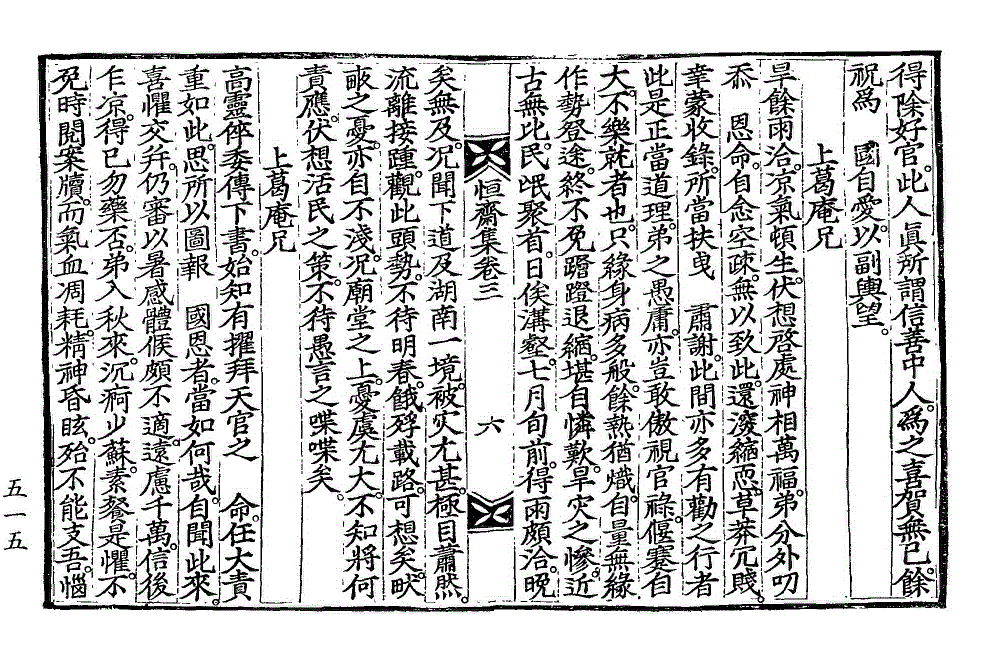 得除好官。此人真所谓信善中人。为之喜贺无已。馀祝为 国自爱。以副舆望。
得除好官。此人真所谓信善中人。为之喜贺无已。馀祝为 国自爱。以副舆望。上葛庵兄
旱馀雨洽。凉气顿生。伏想启处神相万福。弟分外叨忝 恩命。自念空疏。无以致此。还深缩恧。草莽冗贱。幸蒙收录。所当扶曳 肃谢。此间亦多有劝之行者此是正当道理。弟之愚庸。亦岂敢傲视官禄。偃蹇自大。不乐就者也。只缘身病多般。馀热犹炽。自量无缘作势登途。终不免蹭蹬退缩。堪自怜叹。旱灾之惨。近古无比。民氓聚首。曰俟沟壑。七月旬前。得雨颇洽。晚矣无及。况闻下道及湖南一境。被灾尤甚。极目萧然。流离接踵。观此头势。不待明春。饿殍载路。可想矣。畎亩之忧。亦自不浅。况庙堂之上。忧虞尤大。不知将何责应。伏想活民之策。不待愚言之喋喋矣。
上葛庵兄
高灵倅委传下书。始知有擢拜天官之 命。任大责重如此。思所以图报 国恩者。当如何哉。自闻此来。喜惧交并。仍审以暑感体候颇不适。远虑千万。信后乍凉。得已勿药否。弟入秋来。沈痾少苏。素餐是惧。不免时阅案牍。而气血凋耗。精神昏眩。殆不能支吾。恼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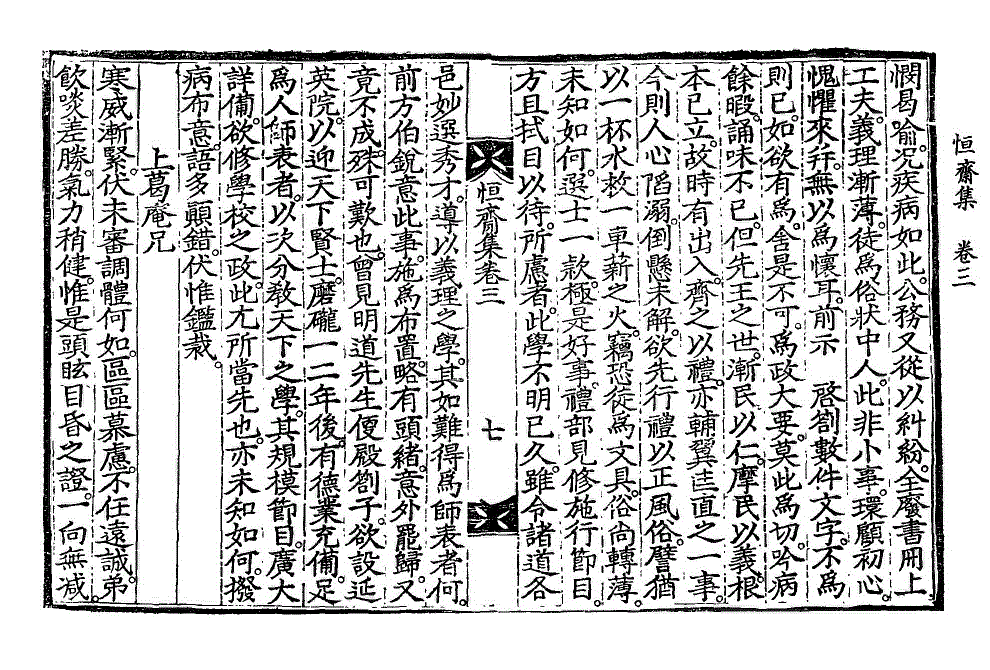 悯曷喻。况疾病如此。公务又从以纠纷。全废书册上工夫。义理渐薄。徒为俗状中人。此非小事。环顾初心。愧惧来并。无以为怀耳。前示 启劄数件文字。不为则已。如欲有为。舍是不可。为政大要。莫此为切。吟病馀暇。诵味不已。但先王之世。渐民以仁。摩民以义。根本已立。故时有出入。齐之以礼。亦辅翼匡直之一事。今则人心陷溺。倒悬未解。欲先行礼以正风俗。譬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窃恐徒为文具。俗尚转薄。未知如何。选士一款。极是好事。礼部见修施行节目。方且拭目以待。所虑者。此学不明已久。虽令诸道各邑妙选秀才。导以义理之学。其如难得为师表者何。前方伯锐意此事。施为布置。略有头绪。意外罢归。又竟不成。殊可叹也。曾见明道先生便殿劄子。欲设延英院。以迎天下贤士。磨砻一二年后。有德业充备。足为人师表者。以次分教天下之学。其规模节目。广大详备。欲修学校之政。此尤所当先也。亦未知如何。拨病布意。语多颠错。伏惟鉴裁。
悯曷喻。况疾病如此。公务又从以纠纷。全废书册上工夫。义理渐薄。徒为俗状中人。此非小事。环顾初心。愧惧来并。无以为怀耳。前示 启劄数件文字。不为则已。如欲有为。舍是不可。为政大要。莫此为切。吟病馀暇。诵味不已。但先王之世。渐民以仁。摩民以义。根本已立。故时有出入。齐之以礼。亦辅翼匡直之一事。今则人心陷溺。倒悬未解。欲先行礼以正风俗。譬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窃恐徒为文具。俗尚转薄。未知如何。选士一款。极是好事。礼部见修施行节目。方且拭目以待。所虑者。此学不明已久。虽令诸道各邑妙选秀才。导以义理之学。其如难得为师表者何。前方伯锐意此事。施为布置。略有头绪。意外罢归。又竟不成。殊可叹也。曾见明道先生便殿劄子。欲设延英院。以迎天下贤士。磨砻一二年后。有德业充备。足为人师表者。以次分教天下之学。其规模节目。广大详备。欲修学校之政。此尤所当先也。亦未知如何。拨病布意。语多颠错。伏惟鉴裁。上葛庵兄
寒威渐紧。伏未审调体何如。区区慕虑。不任远诚。弟饮啖差胜。气力稍健。惟是头眩目昏之證。一向无减。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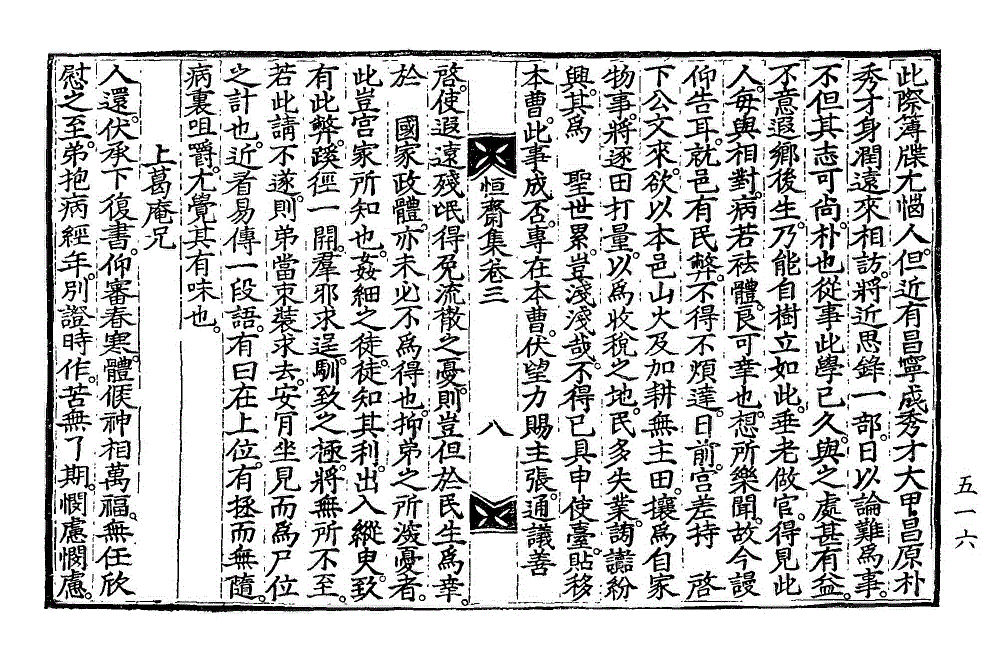 此际簿牒尤恼人。但近有昌宁成秀才大甲,昌原朴秀才身润远来相访。将近思录一部。日以论难为事。不但其志可尚。朴也从事此学已久。与之处甚有益。不意遐乡后生。乃能自树立如此。垂老做官。得见此人。每与相对。病若祛体。良可幸也。想所乐闻。故今谩仰告耳。就邑有民弊。不得不烦达。日前。宫差持 启下公文来。欲以本邑山火及加耕无主田。攘为自家物事。将逐田打量。以为收税之地。民多失业。谤讟纷兴。其为 圣世累。岂浅浅哉。不得已具申使台。贴移本曹。此事成否。专在本曹。伏望力赐主张。通议善 启。使遐远残氓得免流散之忧。则岂但于民生为幸。于 国家政体。亦未必不为得也。抑弟之所深忧者。此岂宫家所知也。奸细之徒。徒知其利。出入纵臾。致有此弊。蹊径一开。群邪求逞。驯致之极。将无所不至。若此请不遂。则弟当束装求去。安肯坐见而为尸位之计也。近看易传一段语。有曰在上位。有拯而无随。病里咀嚼。尤觉其有味也。
此际簿牒尤恼人。但近有昌宁成秀才大甲,昌原朴秀才身润远来相访。将近思录一部。日以论难为事。不但其志可尚。朴也从事此学已久。与之处甚有益。不意遐乡后生。乃能自树立如此。垂老做官。得见此人。每与相对。病若祛体。良可幸也。想所乐闻。故今谩仰告耳。就邑有民弊。不得不烦达。日前。宫差持 启下公文来。欲以本邑山火及加耕无主田。攘为自家物事。将逐田打量。以为收税之地。民多失业。谤讟纷兴。其为 圣世累。岂浅浅哉。不得已具申使台。贴移本曹。此事成否。专在本曹。伏望力赐主张。通议善 启。使遐远残氓得免流散之忧。则岂但于民生为幸。于 国家政体。亦未必不为得也。抑弟之所深忧者。此岂宫家所知也。奸细之徒。徒知其利。出入纵臾。致有此弊。蹊径一开。群邪求逞。驯致之极。将无所不至。若此请不遂。则弟当束装求去。安肯坐见而为尸位之计也。近看易传一段语。有曰在上位。有拯而无随。病里咀嚼。尤觉其有味也。上葛庵兄
人还。伏承下复书。仰审春寒。体候神相万福。无任欣慰之至。弟抱病经年。别證时作。苦无了期。悯虑悯虑。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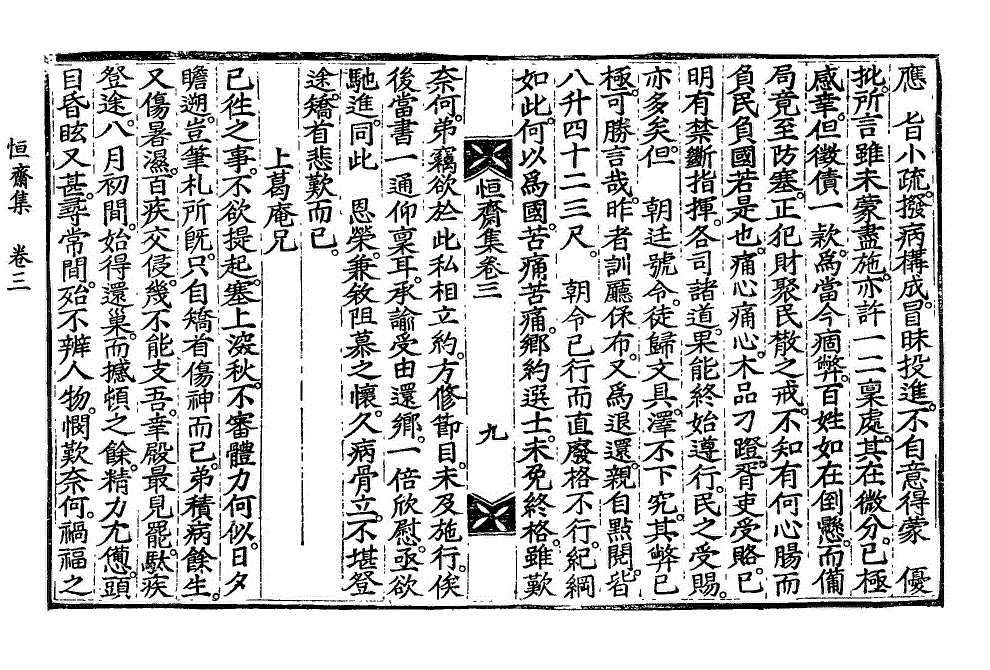 应 旨小疏。拨病构成。冒昧投进。不自意得蒙 优批。所言虽未蒙尽施。亦许一二禀处。其在微分。已极感幸。但徵债一款。为当今痼弊。百姓如在倒悬。而备局竟至防塞。正犯财聚民散之戒。不知有何心肠而负民负国若是也。痛心痛心。木品刁蹬。胥吏受赂。已明有禁断指挥。各司诸道。果能终始遵行。民之受赐。亦多矣。但 朝廷号令。徒归文具。泽不下究。其弊已极。可胜言哉。昨者训厅保布。又为退还。亲自点阅。皆八升四十二三尺。 朝令已行而直废格不行。纪纲如此。何以为国。苦痛苦痛。乡约选士。未免终格。虽叹奈何。弟窃欲于此私相立约。方修节目。未及施行。俟后当书一通仰禀耳。承谕受由还乡。一倍欣慰。亟欲驰进。同此 恩荣。兼叙阻慕之怀。久病骨立。不堪登途。矫首悲叹而已。
应 旨小疏。拨病构成。冒昧投进。不自意得蒙 优批。所言虽未蒙尽施。亦许一二禀处。其在微分。已极感幸。但徵债一款。为当今痼弊。百姓如在倒悬。而备局竟至防塞。正犯财聚民散之戒。不知有何心肠而负民负国若是也。痛心痛心。木品刁蹬。胥吏受赂。已明有禁断指挥。各司诸道。果能终始遵行。民之受赐。亦多矣。但 朝廷号令。徒归文具。泽不下究。其弊已极。可胜言哉。昨者训厅保布。又为退还。亲自点阅。皆八升四十二三尺。 朝令已行而直废格不行。纪纲如此。何以为国。苦痛苦痛。乡约选士。未免终格。虽叹奈何。弟窃欲于此私相立约。方修节目。未及施行。俟后当书一通仰禀耳。承谕受由还乡。一倍欣慰。亟欲驰进。同此 恩荣。兼叙阻慕之怀。久病骨立。不堪登途。矫首悲叹而已。上葛庵兄
已往之事。不欲提起。塞上深秋。不审体力何似。日夕瞻溯。岂笔札所既。只自矫首伤神而已。弟积病馀生。又伤暑湿。百疾交侵。几不能支吾。幸殿最见罢。驮疾登途。八月初间。始得还巢。而撼顿之馀。精力尤惫。头目昏眩又甚。寻常间。殆不辨人物。悯叹奈何。祸福之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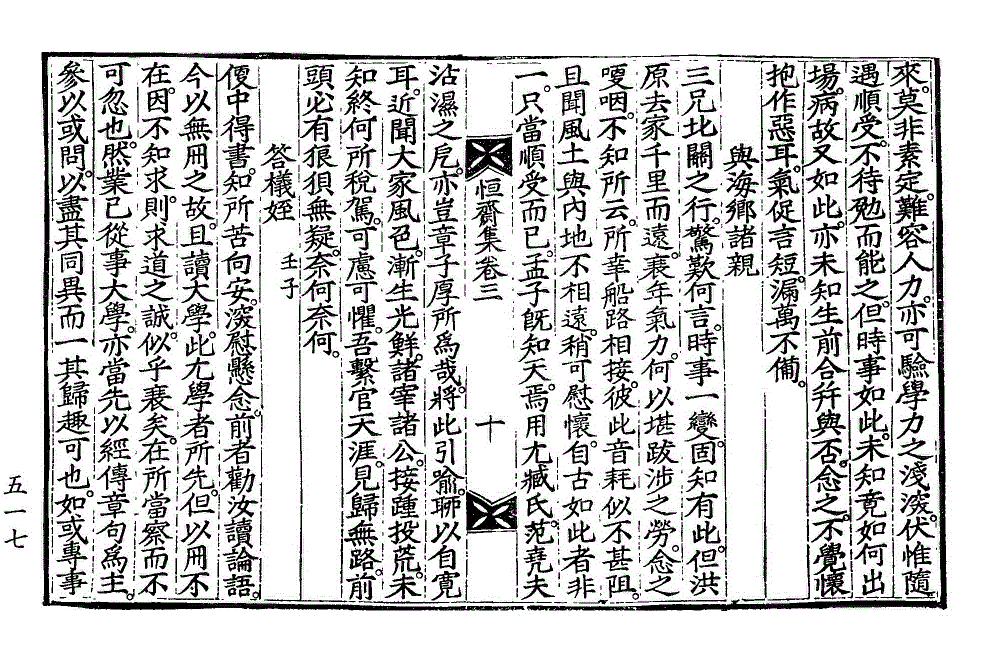 来。莫非素定。难容人力。亦可验学力之浅深。伏惟随遇顺受。不待勉而能之。但时事如此。未知竟如何出场。病故又如此。亦未知生前合并与否。念之。不觉怀抱作恶耳。气促言短。漏万不备。
来。莫非素定。难容人力。亦可验学力之浅深。伏惟随遇顺受。不待勉而能之。但时事如此。未知竟如何出场。病故又如此。亦未知生前合并与否。念之。不觉怀抱作恶耳。气促言短。漏万不备。与海乡诸亲
三兄北关之行。惊叹何言。时事一变。固知有此。但洪原去家千里而远。衰年气力。何以堪跋涉之劳。念之哽咽。不知所云。所幸船路相接。彼此音耗似不甚阻。且闻风土与内地不相远。稍可慰怀。自古如此者非一。只当顺受而已。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范尧夫沾湿之厄。亦岂章子厚所为哉。将此引喻。聊以自宽耳。近闻大家风色。渐生光鲜。诸宰诸公。接踵投荒。未知终何所税驾。可虑可惧。吾系官天涯。见归无路。前头必有狼狈无疑。奈何奈何。
答舣侄(壬子)
便中得书。知所苦向安。深慰悬念。前者劝汝读论语。今以无册之故。且读大学。此尤学者所先。但以册不在。因不知求。则求道之诚。似乎衰矣。在所当察而不可忽也。然业已从事大学。亦当先以经传章句为主。参以或问。以尽其同异而一其归趣可也。如或专事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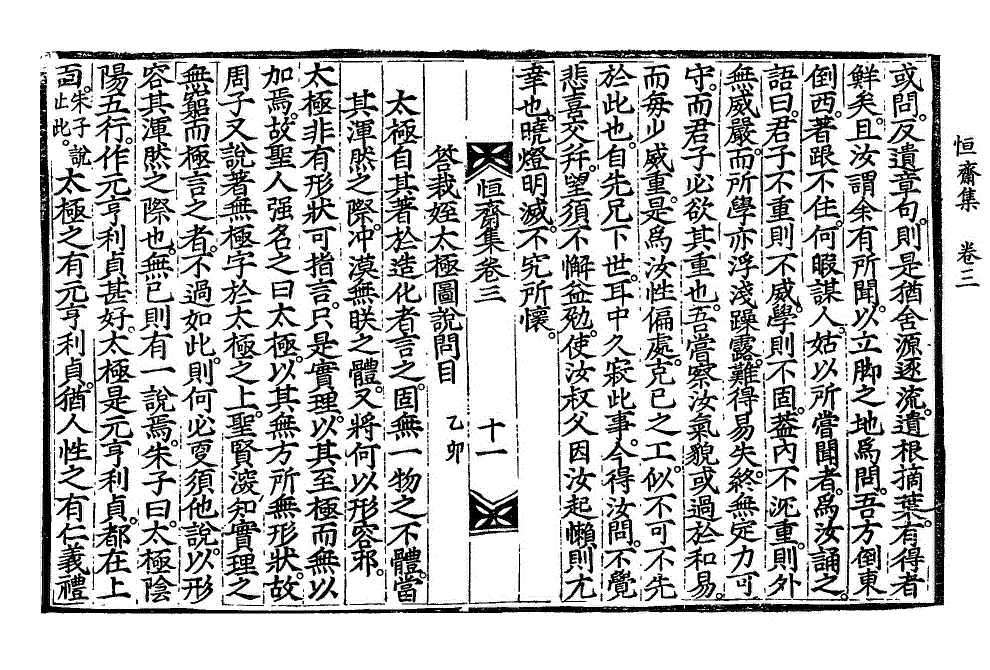 或问。反遗章句。则是犹舍源逐流。遗根摘叶。有得者鲜矣。且汝谓余有所闻。以立脚之地为问。吾方倒东倒西。著跟不住。何暇谋人。姑以所尝闻者。为汝诵之。语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盖内不沈重。则外无威严。而所学亦浮浅躁露。难得易失。终无定力可守。而君子必欲其重也。吾尝察汝气貌或过于和易。而每少威重。是为汝性偏处。克己之工。似不可不先于此也。自先兄下世。耳中久寂此事。今得汝问。不觉悲喜交并。望须不懈益勉。使汝叔父因汝起懒则尤幸也。晓灯明灭。不究所怀。
或问。反遗章句。则是犹舍源逐流。遗根摘叶。有得者鲜矣。且汝谓余有所闻。以立脚之地为问。吾方倒东倒西。著跟不住。何暇谋人。姑以所尝闻者。为汝诵之。语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盖内不沈重。则外无威严。而所学亦浮浅躁露。难得易失。终无定力可守。而君子必欲其重也。吾尝察汝气貌或过于和易。而每少威重。是为汝性偏处。克己之工。似不可不先于此也。自先兄下世。耳中久寂此事。今得汝问。不觉悲喜交并。望须不懈益勉。使汝叔父因汝起懒则尤幸也。晓灯明灭。不究所怀。答栽侄太极图说问目(乙卯)
太极自其著于造化者言之。固无一物之不体。当其浑然之际。冲漠无眹之体。又将何以形容耶。
太极非有形状可指言。只是实理。以其至极而无以加焉。故圣人强名之曰太极。以其无方所无形状。故周子又说著无极字于太极之上。圣贤深知实理之无穷而极言之者。不过如此。则何必更须他说。以形容其浑然之际也。无己则有一说焉。朱子曰。太极阴阳五行。作元亨利贞甚好。太极是元亨利贞。都在上面。(朱子说止此。)太极之有元亨利贞。犹人性之有仁义礼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8L 页
 智也。此实理之可指言者。不于此求之。必欲形容其浑然之际而驰心于空荡之地。则吾见其去道益远。而终无端的可据处矣。
智也。此实理之可指言者。不于此求之。必欲形容其浑然之际而驰心于空荡之地。则吾见其去道益远。而终无端的可据处矣。五行一也。何以有生行之异乎。且黄勉斋所论阴阳稚盛之说。与朱子说不同。何耶。
五行生行之序。虽若有两样。皆天地自然之理。徐而玩之。自当通晓矣。阴阳稚盛。朱子勉斋各据所见。然窃意勉斋为密。孔子所谓后生可畏者。此类可见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气质。而太极之体。无不各具于其中。则谓天下之物洪纤巨细。皆具此阴阳五行许多道理可乎。
太极即理也。随其气质而此理具焉。此理既具则无非全体矣。何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气质。而以各具者言之。一物之中。莫不各有阴阳五行许多道理。阴阳五行之理。即太极浑然之体也。此说吾尝论辨得之。而犹未敢自信。更愿详之。
神即心之知觉耶。其谓发于阳者何耶。心或以阴阳言。或以太极言。或以理气之合言之。何耶。
所谓神者。乃物之灵。而即所以知觉者。非知觉之谓也。人之生也。气质而已。气之灵为神。质之精为知。气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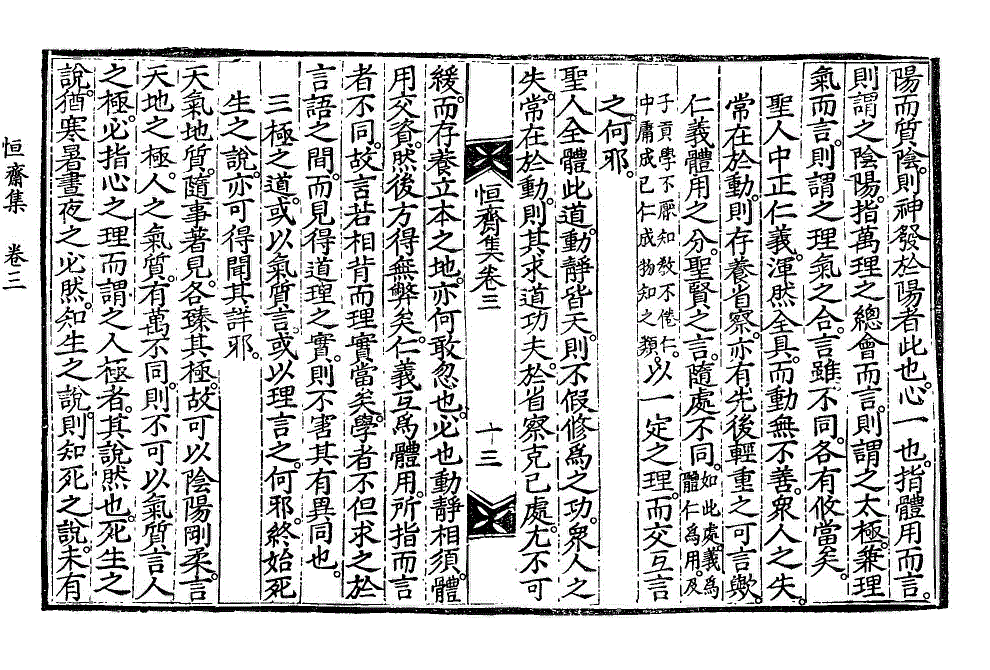 阳而质阴。则神发于阳者此也。心一也。指体用而言。则谓之阴阳。指万理之总会而言。则谓之太极。兼理气而言。则谓之理气之合。言虽不同。各有攸当矣。
阳而质阴。则神发于阳者此也。心一也。指体用而言。则谓之阴阳。指万理之总会而言。则谓之太极。兼理气而言。则谓之理气之合。言虽不同。各有攸当矣。圣人中正仁义。浑然全具。而动无不善。众人之失。常在于动。则存养省察。亦有先后轻重之可言欤。仁义体用之分。圣贤之言。随处不同。(如此处。义为体仁为用。及子贡学不厌知教不倦仁。中庸成己仁成物知之类。)以一定之理。而交互言之。何耶。
圣人全体此道。动静皆天。则不假修为之功。众人之失。常在于动。则其求道功夫。于省察克己处。尤不可缓。而存养立本之地。亦何敢忽也。必也动静相须。体用交资。然后方得无弊矣。仁义互为体用。所指而言者不同。故言若相背而理实当矣。学者不但求之于言语之间。而见得道理之实。则不害其有异同也。
三极之道。或以气质言。或以理言之。何耶。终始死生之说。亦可得闻其详耶。
天气地质。随事著见。各臻其极。故可以阴阳刚柔。言天地之极。人之气质。有万不同。则不可以气质言人之极。必指心之理而谓之人极者。其说然也。死生之说。犹寒暑昼夜之必然。知生之说。则知死之说。未有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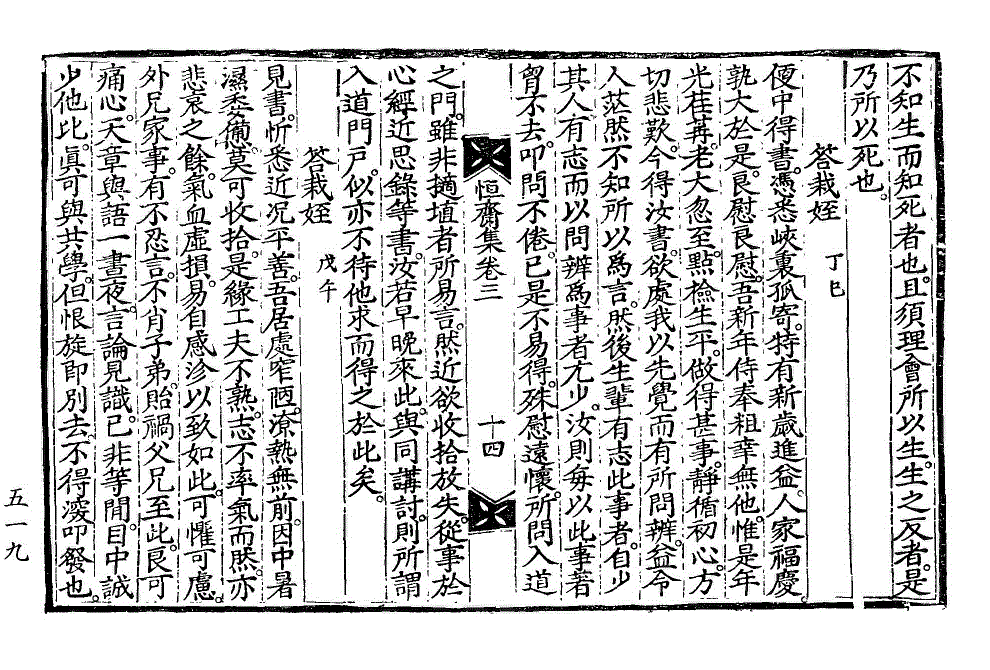 不知生而知死者也。且须理会所以生。生之反者。是乃所以死也。
不知生而知死者也。且须理会所以生。生之反者。是乃所以死也。答栽侄(丁巳)
便中得书。凭悉峡里孤寄。特有新岁进益。人家福庆。孰大于是。良慰良慰。吾新年侍奉粗幸无他。惟是年光荏苒。老大忽至。点检生平。做得甚事。静循初心。方切悲叹。今得汝书。欲处我以先觉而有所问辨。益令人茫然不知所以为言。然后生辈有志此事者。自少其人有志而以问辨为事者尤少。汝则每以此事著胸不去。叩问不倦。已是不易得。殊慰远怀。所问入道之门。虽非擿埴者所易言。然近欲收拾放失。从事于心经,近思录等书。汝若早晚来此。与同讲讨。则所谓入道门户。似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答栽侄(戊午)
见书。忻悉近况平善。吾居处窄陋。潦热无前。因中暑湿委惫。莫可收拾。是缘工夫不熟。志不率气而然。亦悲哀之馀。气血虚损。易自感沴以致如此。可惧可虑。外兄家事。有不忍言。不肖子弟。贻祸父兄至此。良可痛心。天章与语一昼夜。言论见识。已非等閒。目中诚少他比。真可与共学。但恨旋即别去。不得深叩发也。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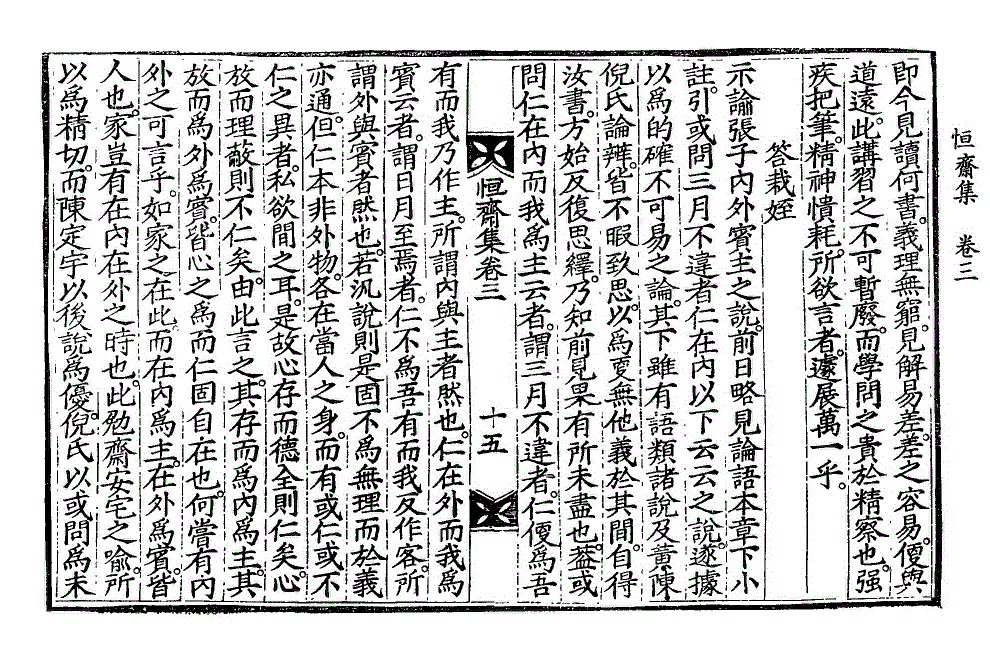 即今见读何书。义理无穷。见解易差。差之容易。便与道远。此讲习之不可暂废。而学问之贵于精察也。强疾把笔。精神愦耗。所欲言者。遽展万一乎。
即今见读何书。义理无穷。见解易差。差之容易。便与道远。此讲习之不可暂废。而学问之贵于精察也。强疾把笔。精神愦耗。所欲言者。遽展万一乎。答栽侄
示谕张子内外宾主之说。前日略见论语本章下小注。引或问三月不违者仁在内以下云云之说。遂据以为的确不可易之论。其下虽有语类诸说及黄,陈,倪氏论辨。皆不暇致思。以为更无他义于其间。自得汝书。方始反复思绎。乃知前见果有所未尽也。盖或问仁在内而我为主云者。谓三月不违者。仁便为吾有而我乃作主。所谓内与主者然也。仁在外而我为宾云者。谓日月至焉者。仁不为吾有而我反作客。所谓外与实者然也。若汎说则是固不为无理而于义亦通。但仁本非外物。各在当人之身。而有或仁或不仁之异者。私欲间之耳。是故心存而德全则仁矣。心放而理蔽则不仁矣。由此言之。其存而为内为主。其放而为外为宾。皆心之为而仁固自在世。何尝有内外之可言乎。如家之在此。而在内为主。在外为宾。皆人也。家岂有在内在外之时也。此勉斋安宅之喻。所以为精切。而陈定宇以后说为优。倪氏以或问为未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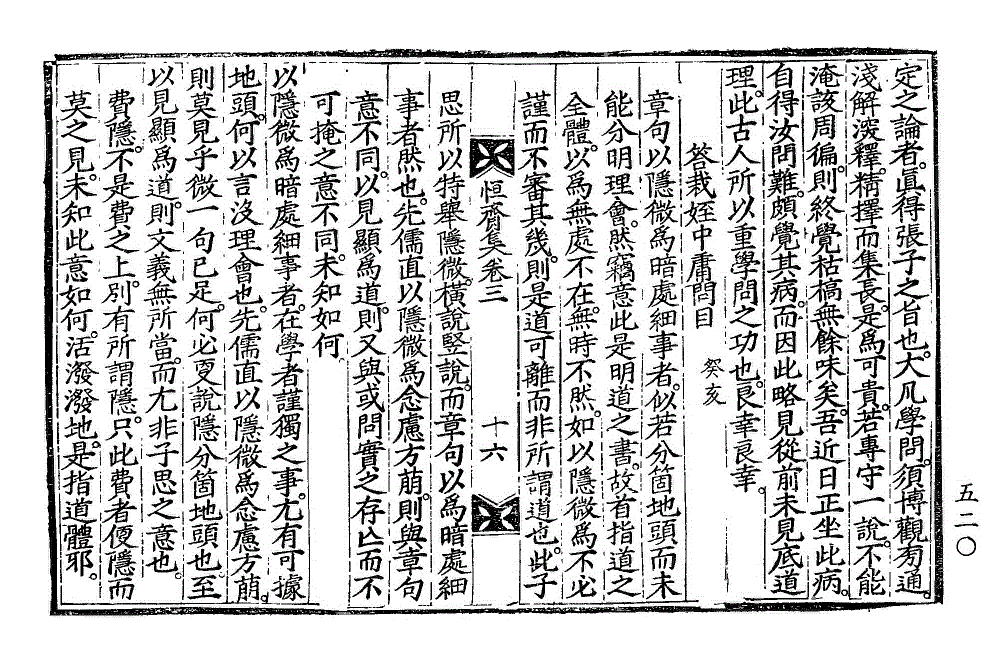 定之论者。真得张子之旨也。大凡学问。须博观旁通。浅解深释。精择而集长。是为可贵。若专守一说。不能淹该周遍。则终觉枯槁无馀味矣。吾近日正坐此病。自得汝问难。颇觉其病。而因此略见从前未见底道理。此古人所以重学问之功也。良幸良幸。
定之论者。真得张子之旨也。大凡学问。须博观旁通。浅解深释。精择而集长。是为可贵。若专守一说。不能淹该周遍。则终觉枯槁无馀味矣。吾近日正坐此病。自得汝问难。颇觉其病。而因此略见从前未见底道理。此古人所以重学问之功也。良幸良幸。答栽侄中庸问目(癸亥)
章句以隐微为暗处细事者。似若分个地头而未能分明理会。然窃意此是明道之书。故首指道之全体。以为无处不在。无时不然。如以隐微为不必谨而不审其几。则是道可离而非所谓道也。此子思所以特举隐微。横说竖说。而章句以为暗处细事者然也。先儒直以隐微为念虑方萌。则与章句意不同。以见显为道。则又与或问实之存亡而不可掩之意不同。未知如何。
以隐微为暗处细事者。在学者谨独之事。尤有可据地头。何以言没理会也。先儒直以隐微为念虑方萌。则莫见乎微一句已足。何必更说隐分个地头也。至以见显为道。则文义无所当。而尤非子思之意也。
费隐。不是费之上。别有所谓隐。只此费者便隐而莫之见。未知此意如何。活泼泼地。是指道体耶。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1H 页
 只此费者便隐而莫之见也。说得极是。活泼泼地者。指道之体用而言也。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间者。无少欠缺。无少间断。流动充满。汪洋浩大。此活泼泼意思也。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为同此活泼泼地者。复指心之体用而言也。
只此费者便隐而莫之见也。说得极是。活泼泼地者。指道之体用而言也。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间者。无少欠缺。无少间断。流动充满。汪洋浩大。此活泼泼意思也。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为同此活泼泼地者。复指心之体用而言也。鬼神即气也。章句直以为费隐。何耶。特因彼以明此耶。无非实者之实字。似不当作实理看。如何。
此特以鬼神。明道之费隐也。实字不必作实理看。
以己度人。未尝不同与己之所以责人。何以为道不远人之说耶。
人之生也。与道俱生。故人心所安。则不远于道。但责己则暗。责人则明。君子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焉。此不远人以为道之事也。
诚者自成章。有实心实理之分耶。理非可尽之物。而曰尽曰澌尽。何耶。合内外者。己与物为内外而仁知不外于吾心。故云然耶。
诚者自成。以实心而言之也。诚者物之终始。兼实理与实心而言之也。至诚之为贵一句。则专就实心处而明之也。澌尽云者。犹云消灭也。理之本体。非可尽之物。而以人物所得言之。则岂无消灭之时也。合内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1L 页
 外之说。以成己成物言之。则虽若有内外亲疏之分。以仁知同为吾性之德言之。则非有内外之分也。来说得矣。
外之说。以成己成物言之。则虽若有内外亲疏之分。以仁知同为吾性之德言之。则非有内外之分也。来说得矣。尊德性以下。不曰致知力行。而必曰存心致知。何耶。如崇礼道中庸。尤似属行。而必为致知之属。何也。窃意此章本以道之大小言。故必曰存心然后可以全其本体而尽其大。必曰致知然后可以随事精察而尽其小。而所谓力行。未尝不在致知之中。未知此意如何。或以存心属修德。致知属凝道。此说如何。
知行之不可偏废。如轮翼之不可独行。安知存心非行也。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安知非致知之属也。以存心致知。分属修德凝道未安。存心致知。乃修德之事。而德之至则至道凝焉。
至圣之德。何以言用。至诚之道。何以言体。或以未发之中。为不显之德。戒惧为不显之敬。笃恭而天下平。为中和位育之事。分属至此。莫太牵合否。
道是公共底。德是修为底。以此言之。道其本而德其用乎。不显。乃幽深玄远之意。下文笃恭。正所谓不显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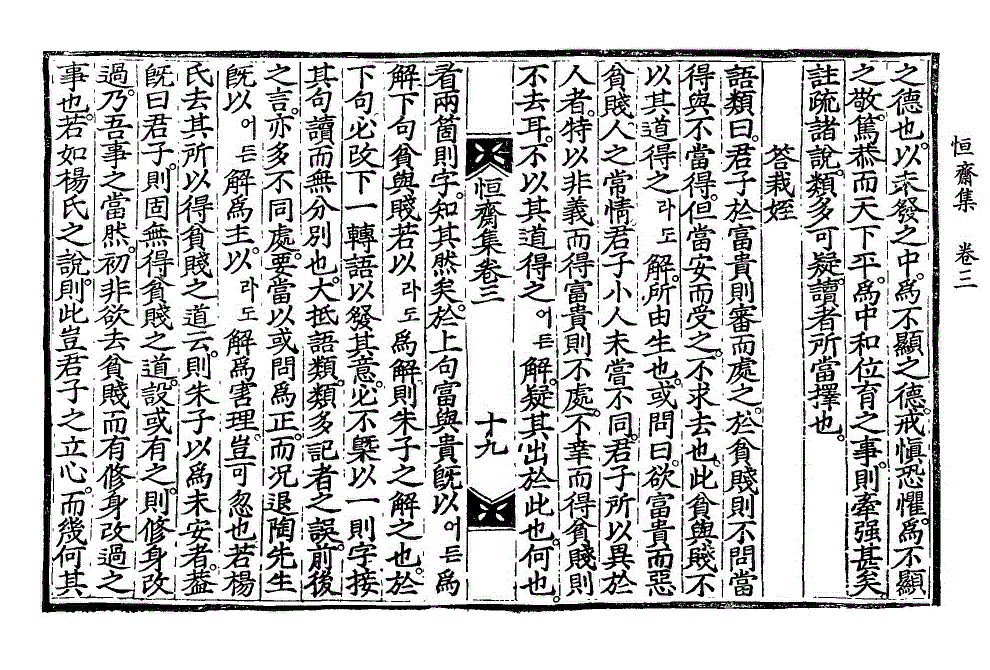 之德也。以未发之中。为不显之德。戒慎恐惧。为不显之敬。笃恭而天下平。为中和位育之事。则牵强甚矣。注疏诸说。类多可疑。读者所当择也。
之德也。以未发之中。为不显之德。戒慎恐惧。为不显之敬。笃恭而天下平。为中和位育之事。则牵强甚矣。注疏诸说。类多可疑。读者所当择也。答栽侄
语类曰。君子于富贵则审而处之。于贫贱则不问当得与不当得。但当安而受之。不求去也。此贫与贱不以其道得之(라도)解。所由生也。或问曰。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特以非义而得富贵则不处。不幸而得贫贱则不去耳。不以其道得之(어든)解。疑其出于此也。何也。看两个则字。知其然矣。于上句富与贵既以(어든)为解。下句贫与贱若以(라도)为解。则朱子之解之也。于下句。必改下一转语以发其意。必不槩以一则字接其句读而无分别也。大抵语类。类多记者之误。前后之言。亦多不同处。要当以或问为正。而况退陶先生既以(어든)解为主。以(라도)解为害理。岂可忽也。若杨氏去其所以得贫贱之道云。则朱子以为未安者。盖既曰君子。则固无得贫贱之道。设或有之。则修身改过。乃吾事之当然。初非欲去贫贱而有修身改过之事也。若如杨氏之说。则此岂君子之立心。而几何其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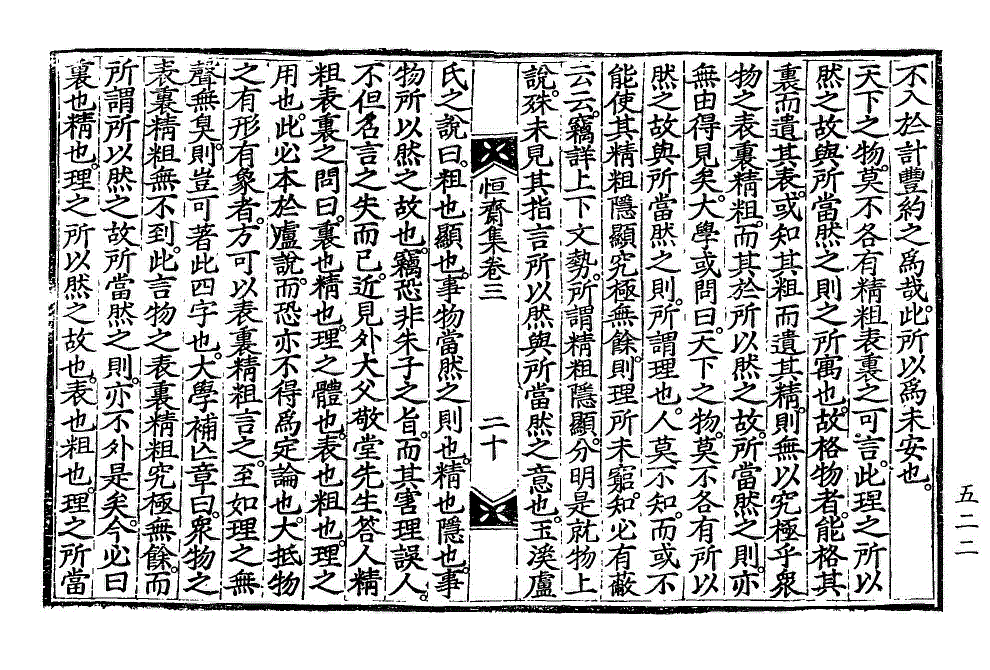 不入于计丰约之为哉。此所以为未安也。
不入于计丰约之为哉。此所以为未安也。天下之物。莫不各有精粗表里之可言。此理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之所寓也。故格物者。能格其里而遗其表。或知其粗而遗其精。则无以究极乎众物之表里精粗。而其于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亦无由得见矣。大学或问曰。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隐显究极无馀。则理所未穷。知必有蔽云云。窃详上下文势。所谓精粗隐显。分明是就物上说。殊未见其指言所以然与所当然之意也。玉溪卢氏之说曰。粗也显也。事物当然之则也。精也隐也。事物所以然之故也。窃恐非朱子之旨。而其害理误人。不但名言之失而已。近见外大父敬堂先生答人精粗表里之问曰。里也精也。理之体也。表也粗也。理之用也。此必本于卢说。而恐亦不得为定论也。大抵物之有形有象者。方可以表里精粗言之。至如理之无声无臭。则岂可著此四字也。大学补亡章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此言物之表里精粗究极无馀。而所谓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亦不外是矣。今必曰里也精也。理之所以然之故也。表也粗也。理之所当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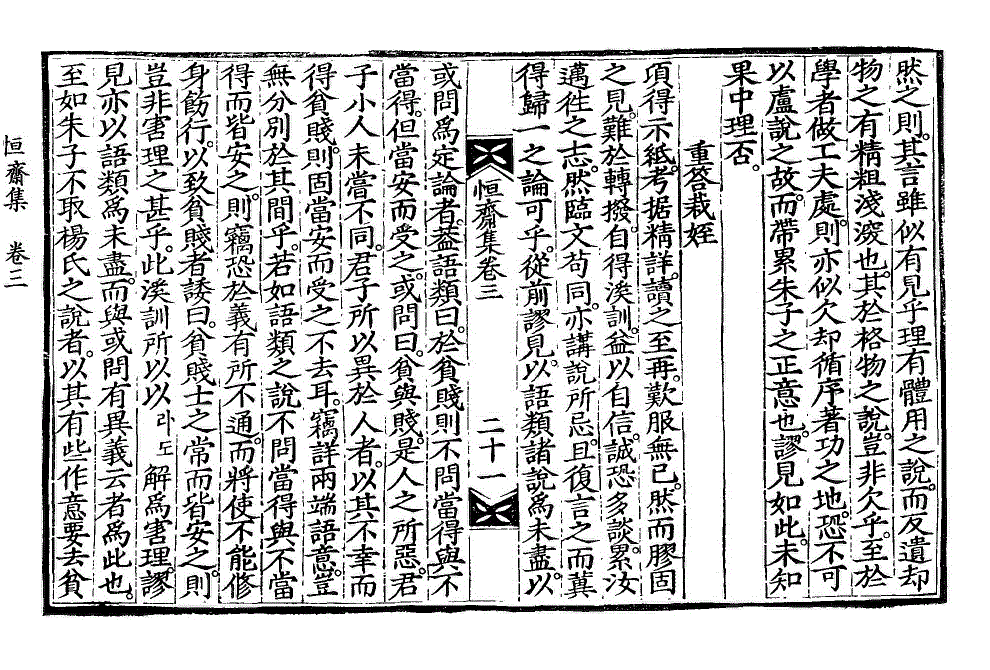 然之则。其言虽似有见乎理有体用之说。而反遗却物之有精粗浅深也。其于格物之说。岂非欠乎。至于学者做工夫处。则亦似欠却循序著功之地。恐不可以卢说之故。而带累朱子之正意也。谬见如此。未如果中理否。
然之则。其言虽似有见乎理有体用之说。而反遗却物之有精粗浅深也。其于格物之说。岂非欠乎。至于学者做工夫处。则亦似欠却循序著功之地。恐不可以卢说之故。而带累朱子之正意也。谬见如此。未如果中理否。重答栽侄
顷得示纸。考据精详。读之至再。叹服无已。然而胶固之见。难于转拨。自得溪训。益以自信。诚恐多谈。累汝迈往之志。然临文苟同。亦讲说所忌。且复言之而冀得归一之论可乎。从前谬见。以语类诸说为未尽。以或问为定论者。盖语类曰。于贫贱则不问当得与不当得。但当安而受之。或问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君子小人未尝不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不幸而得贫贱。则固当安而受之不去耳。窃详两端语意。岂无分别于其间乎。若如语类之说不问当得与不当得而皆安之。则窃恐于义有所不通。而将使不能修身饬行。以致贫贱者诿曰。贫贱士之常而皆安之。则岂非害理之甚乎。此溪训所以以(라도)解为害理。谬见亦以语类为未尽。而与或问有异义云者为此也。至如朱子不取杨氏之说者。以其有些作意要去贫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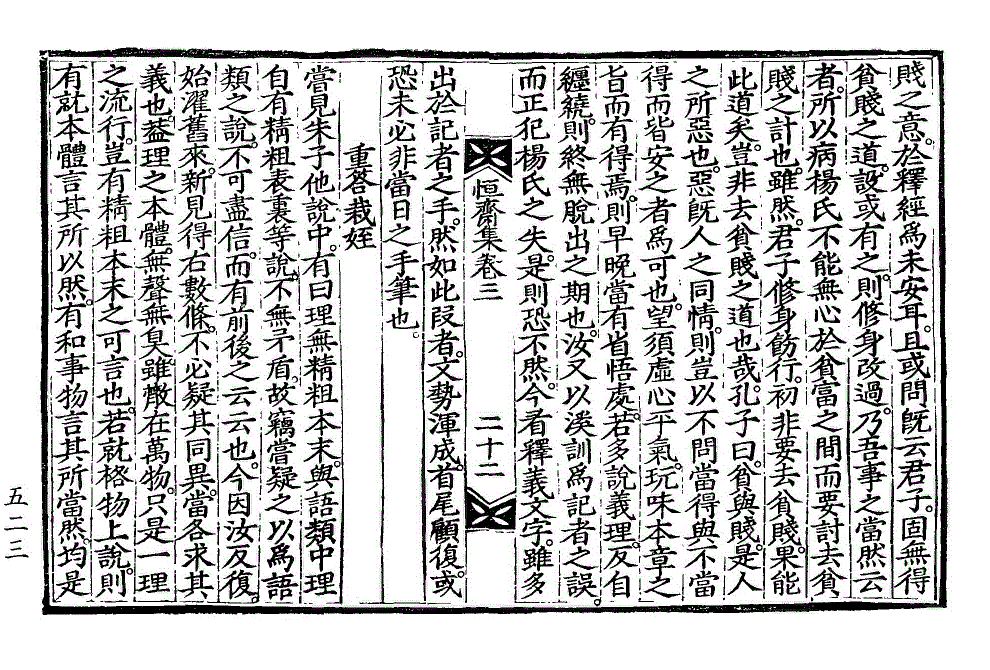 贱之意。于释经为未安耳。且或问既云君子。固无得贫贱之道。设或有之。则修身改过。乃吾事之当然云者。所以病杨氏不能无心于贫富之间而要讨去贫贱之计也。虽然。君子修身饬行。初非要去贫贱。果能此道矣。岂非去贫贱之道也哉。孔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恶既人之同情。则岂以不问当得与不当得而皆安之者为可也。望须虚心平气。玩味本章之旨而有得焉。则早晚当有省悟处。若多说义理。反自缠绕。则终无脱出之期也。汝又以溪训为记者之误。而正犯杨氏之失。是则恐不然。今看释义文字。虽多出于记者之手。然如此段者。文势浑成。首尾顾复。或恐未必非当日之手笔也。
贱之意。于释经为未安耳。且或问既云君子。固无得贫贱之道。设或有之。则修身改过。乃吾事之当然云者。所以病杨氏不能无心于贫富之间而要讨去贫贱之计也。虽然。君子修身饬行。初非要去贫贱。果能此道矣。岂非去贫贱之道也哉。孔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恶既人之同情。则岂以不问当得与不当得而皆安之者为可也。望须虚心平气。玩味本章之旨而有得焉。则早晚当有省悟处。若多说义理。反自缠绕。则终无脱出之期也。汝又以溪训为记者之误。而正犯杨氏之失。是则恐不然。今看释义文字。虽多出于记者之手。然如此段者。文势浑成。首尾顾复。或恐未必非当日之手笔也。重答栽侄
尝见朱子他说中。有曰理无精粗本末。与语类中理自有精粗表里等说。不无矛盾。故窃尝疑之以为语类之说。不可尽信。而有前后之云云也。今因汝反复。始濯旧来。新见得右数条。不必疑其同异。当各求其义也。盖理之本体。无声无臭。虽散在万物。只是一理之流行。岂有精粗本末之可言也。若就格物上说。则有就本体言其所以然。有和事物言其所当然。均是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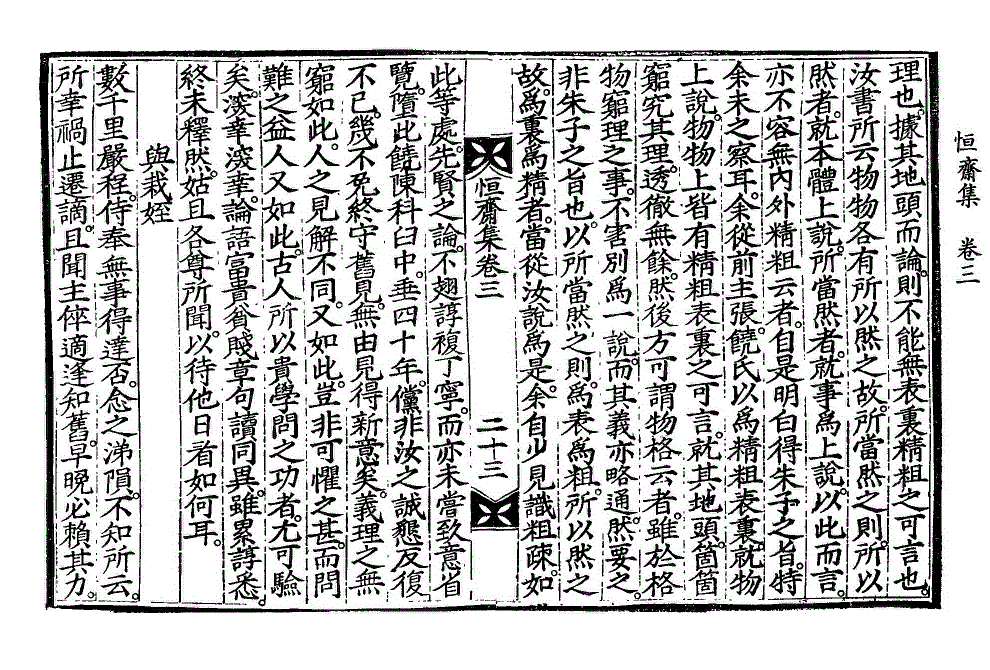 理也。据其地头而论。则不能无表里精粗之可言也。汝书所云物物各有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所以然者。就本体上说。所当然者。就事为上说。以此而言。亦不容无内外精粗云者。自是明白得朱子之旨。特余未之察耳。余从前主张。饶氏以为精粗表里。就物上说。物物上皆有精粗表里之可言。就其地头。个个穷究其理。透彻无馀。然后方可谓物格云者。虽于格物穷理之事。不害别为一说。而其义亦略通。然要之。非朱子之旨也。以所当然之则。为表为粗。所以然之故。为里为精者。当从汝说为是。余自少见识粗疏。如此等处。先贤之论。不翅谆复丁宁。而亦未尝致意省览。堕此饶,陈科臼中。垂四十年。傥非汝之诚恳反复不已。几不免终守旧见。无由见得新意矣。义理之无穷如此。人之见解不同。又如此。岂非可惧之甚。而问难之益人又如此。古人所以贵学问之功者。尤可验矣。深幸深幸。论语富贵贫贱章句读同异。虽累谆悉。终未释然。姑且各尊所闻。以待他日看如何耳。
理也。据其地头而论。则不能无表里精粗之可言也。汝书所云物物各有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所以然者。就本体上说。所当然者。就事为上说。以此而言。亦不容无内外精粗云者。自是明白得朱子之旨。特余未之察耳。余从前主张。饶氏以为精粗表里。就物上说。物物上皆有精粗表里之可言。就其地头。个个穷究其理。透彻无馀。然后方可谓物格云者。虽于格物穷理之事。不害别为一说。而其义亦略通。然要之。非朱子之旨也。以所当然之则。为表为粗。所以然之故。为里为精者。当从汝说为是。余自少见识粗疏。如此等处。先贤之论。不翅谆复丁宁。而亦未尝致意省览。堕此饶,陈科臼中。垂四十年。傥非汝之诚恳反复不已。几不免终守旧见。无由见得新意矣。义理之无穷如此。人之见解不同。又如此。岂非可惧之甚。而问难之益人又如此。古人所以贵学问之功者。尤可验矣。深幸深幸。论语富贵贫贱章句读同异。虽累谆悉。终未释然。姑且各尊所闻。以待他日看如何耳。与栽侄
数千里严程。侍奉无事得达否。念之涕陨。不知所云。所幸祸止迁谪。且闻主倅适逢知旧。早晚必赖其力。
恒斋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5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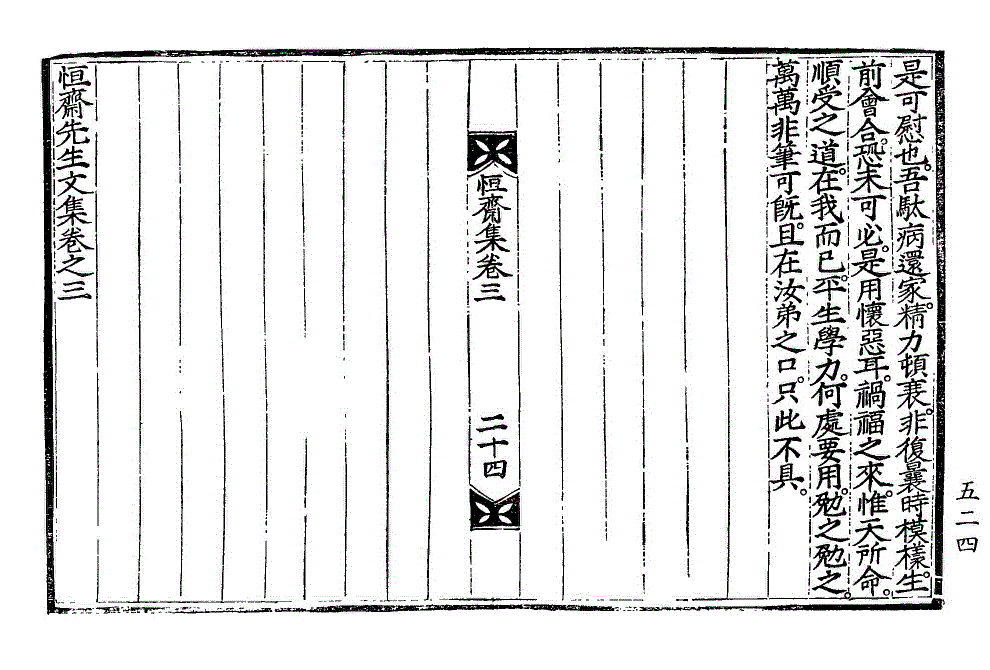 是可慰也。吾驮病还家。精力顿衰。非复曩时模样。生前会合。恐未可必。是用怀恶耳。祸福之来。惟天所命。顺受之道。在我而已。平生学力。何处要用。勉之勉之。万万非笔可既。且在汝弟之口。只此不具。
是可慰也。吾驮病还家。精力顿衰。非复曩时模样。生前会合。恐未可必。是用怀恶耳。祸福之来。惟天所命。顺受之道。在我而已。平生学力。何处要用。勉之勉之。万万非笔可既。且在汝弟之口。只此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