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书
书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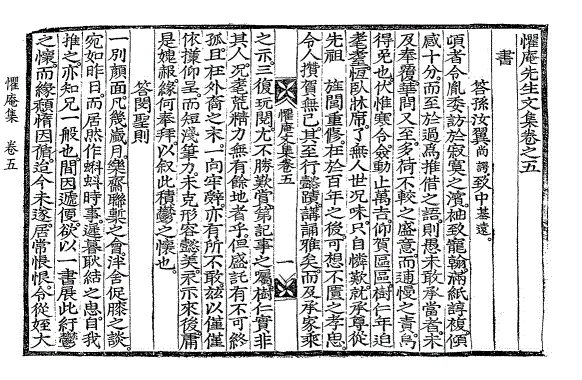 答孙汝翼(尚谔),致中(基远)。
答孙汝翼(尚谔),致中(基远)。顷者令胤委访于寂寞之滨。袖致宠翰。满纸谆复。倾感十分。而至于过为推借之语。则愚未敢承当者。未及奉覆。华问又至。多荷不较之盛意。而逋慢之责。乌得免也。伏惟寒令。佥动止万吉。仰贺区区。树仁年迫耄耋。恒卧床席。了无人世况味。只自怜叹。就承尊从先祖 旌闾重修。在于百年之后。可想不匮之孝思。令人攒贺无已。其至行懿迹。讲诵雅矣。而及承家乘之示。三复玩阅。尤不胜叹赏。第记事之嘱。树仁实非其人。况耄荒精力无有馀地者乎。但盛托有不可终孤。且在外裔之末。一向牢辞。亦有所不敢。玆以仅仅依㨾仰呈。而短浅笔力。未克形容懿美。永示来后。庸是愧赧。缘何奉拜。以叙此积郁之怀也。
答闵圣则
一别颜面。凡几岁月。乐斋联椠之会。泮舍促膝之谈。宛如昨日。而居然作蝌蚪时事。迟暮耿结之思。自我推之。亦知兄一般也。间因递便。欲以一书展此纡郁之怀。而缘颓惰因循。迨今未遂。居常怅恨。令从侄大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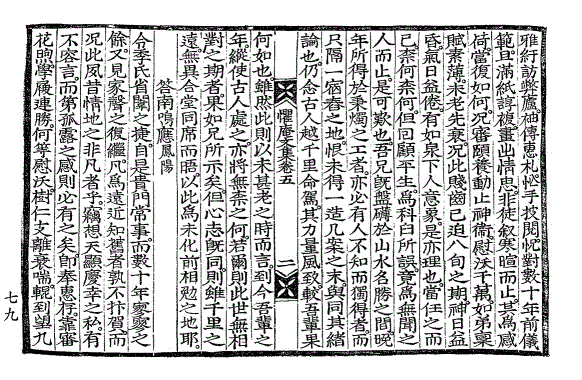 雅纡访弊庐。袖传惠札。忙手披阅。恍对数十年前仪范。且满纸谆复。画出情思。非徒叙寒暄而止。其为感荷。当复如何。况审颐养动止神卫。慰沃千万。如弟禀赋素薄。未老先衰。况此贱齿已迫八旬之期。神日益昏。气日益倦。有如泉下人意象。是亦理也。当任之而已。柰何柰何。但回顾平生。为科臼所误。竟为无闻之人而止。是可叹也。吾兄既盘礴于山水名胜之间。晚年所得于秉烛之工者。亦必有人不知而独得者。而只隔一宿舂之地。恨未得一造几案之末。与同其绪论也。仍念古人越千里命驾。其力量风致。较吾辈果何如也。虽然此则以未甚老之时而言。到今吾辈之年。纵使古人处之。亦将无柰之何。若尔则此世无相对之期者。果如兄所示矣。但心志既同。则虽千里之远。无异合堂同席而晤。以此为未化前相勉之地耶。
雅纡访弊庐。袖传惠札。忙手披阅。恍对数十年前仪范。且满纸谆复。画出情思。非徒叙寒暄而止。其为感荷。当复如何。况审颐养动止神卫。慰沃千万。如弟禀赋素薄。未老先衰。况此贱齿已迫八旬之期。神日益昏。气日益倦。有如泉下人意象。是亦理也。当任之而已。柰何柰何。但回顾平生。为科臼所误。竟为无闻之人而止。是可叹也。吾兄既盘礴于山水名胜之间。晚年所得于秉烛之工者。亦必有人不知而独得者。而只隔一宿舂之地。恨未得一造几案之末。与同其绪论也。仍念古人越千里命驾。其力量风致。较吾辈果何如也。虽然此则以未甚老之时而言。到今吾辈之年。纵使古人处之。亦将无柰之何。若尔则此世无相对之期者。果如兄所示矣。但心志既同。则虽千里之远。无异合堂同席而晤。以此为未化前相勉之地耶。答南鸣应(凤阳)
令季氏省闱之捷。自是贵门常事。而数十年寥寥之馀。又见家声之复继。凡为远近知旧者孰不抃贺。而况此夙昔情地之非凡者乎。窃想天显庆幸之私。有不容言。而第孤露之感则必有之矣。即奉惠存。靠审花煦。学履连胜。何等慰沃。树仁支离衰喘。辊到望九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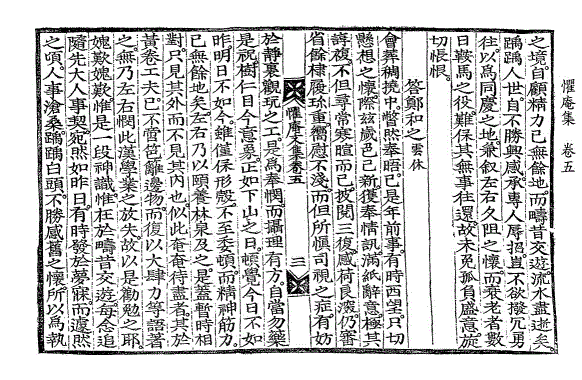 之境。自顾精力已无馀地。而畴昔交游。流水尽逝矣。踽踽人世。自不胜兴感。承专人辱招。岂不欲拨冗勇往。以为同庆之地。兼叙左右久阻之怀。而衰老者数日鞍马之役。难保其无事往还。故未免孤负盛意。旋切怅恨。
之境。自顾精力已无馀地。而畴昔交游。流水尽逝矣。踽踽人世。自不胜兴感。承专人辱招。岂不欲拨冗勇往。以为同庆之地。兼叙左右久阻之怀。而衰老者数日鞍马之役。难保其无事往还。故未免孤负盛意。旋切怅恨。答郑和之(云休)
会葬稠挠中。瞥然奉晤。已是年前事。有时西望。只切悬想之怀。际玆岁色已新。获奉情讯。满纸辞意。极其谆复。不但寻常寒暄而已。披阅三复。感荷良深。仍审省馀棣履珍重。向慰不浅。而但所慎司视之症。有妨于静里观玩之工。是为奉悯。而摄理有方。自当勿药是祝。树仁目今意象。正如下山之日。顿觉今日不如昨。明日不如今。虽仅保形壳。不至委顿。而精神筋力。已无馀地矣。左右乃以颐养林泉及之。是盖暂时相对。只见其外而不见其内也。似此奄奄待尽者。其于黄卷工夫。已不啻笆篱边物。而复以大肆力等语著之。无乃左右悯此汉学业之放失。故以是劝勉之耶。愧叹愧叹。惟是一段神识。惟在于畴昔交游。每念追随先大人事契。宛然如昨日。有时发于梦寐。而遽然之顷。人事沧桑。踽踽白头。不胜感旧之怀。所以为执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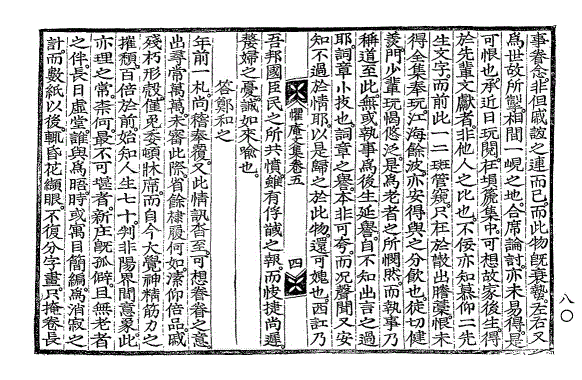 事眷念。非但戚谊之连而已。而此物既衰蛰。左右又为世故所掣。相间一岘之地。合席论讨。亦未易得。是可恨也。承近日玩阅。在埙篪集中。可想故家后生。得于先辈文献者。非他人之比也。不佞亦知慕仰二先生文字。而前此一二斑管窥。只在于散出誊藁。恨未得全集奉玩。江海馀波。亦安得与之分饮也。徒切健羡。门少辈玩愒悠泛。是为老者之所悯然。而执事乃称道至此。无或执事为后生延誉。自不知出言之过耶。词章小技也。词章之誉。本非可夸。而况声闻又安知不过于情耶。以是归之于此物。还可愧也。西讧乃吾邦国臣民之所共愤。虽有俘馘之报。而快捷尚迟。嫠妇之忧。诚如来喻也。
事眷念。非但戚谊之连而已。而此物既衰蛰。左右又为世故所掣。相间一岘之地。合席论讨。亦未易得。是可恨也。承近日玩阅。在埙篪集中。可想故家后生。得于先辈文献者。非他人之比也。不佞亦知慕仰二先生文字。而前此一二斑管窥。只在于散出誊藁。恨未得全集奉玩。江海馀波。亦安得与之分饮也。徒切健羡。门少辈玩愒悠泛。是为老者之所悯然。而执事乃称道至此。无或执事为后生延誉。自不知出言之过耶。词章小技也。词章之誉。本非可夸。而况声闻又安知不过于情耶。以是归之于此物。还可愧也。西讧乃吾邦国臣民之所共愤。虽有俘馘之报。而快捷尚迟。嫠妇之忧。诚如来喻也。答郑和之
年前一札。尚稽奉覆。又此情讯沓至。可想眷眷之意。出寻常万万。未审此际。省馀棣履何如。溸仰倍品。戚残朽形壳。仅免委顿床席。而自今大觉神精筋力之摧颓。百倍于前。始知人生七十。判非阳界间意象。此亦理之常。柰何。最不可堪者。新庄既孤僻。且无老者之伴。长日虚堂。谁与为晤。时或寓目简编。为消寂之计。而数纸以后。辄昏花缬眼。不复分字画。只掩卷长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1H 页
 叹而已。乃者春夏交。幸有南北老友齐会之约。自汶亭而始。继而有良洞文会。仍复设玉山之会而罢。盖前后殆数旬。汶亭玉院之席。则上舍族父亦与焉。是固暮境不易得之事。而但归后寥寂。亦复如前。前头炎节且迫。兀然孤坐。只作苍蝇之伴也。示喻止渊藁评骘。可见尊看文字眼目。迥出等夷。至于推借拙构。则何其爽实之甚也。岂以相爱之至。不知其恶而然耶。每于孤寂中。想执事该博之识颖锐之见。思欲合席讨论。起此衰懒。而远莫之遂。只切怅叹。一番游历仙庄。以及横溪诸胜处。追寻先辈遗迹。乃是宿昔之愿。而顾今年迫桑榆。气力垂尽。且贵中人事倏尔沧桑。便有不忍过西州之意。以是年来此愿。又付之先天者久矣。今执事之示。如是勤挚。反而思之。有如吾执事为之主而与之盘礴。则亦何间于夙世同志之相追也。窃欲以秋末枫菊之辰。为遂此愿。而但老者事。虽时月之近。亦不可指的预期。是则当付之造物者处分也。族弟道叔行录。自是不获辞者。今执事之言又如是。当拔例图之。而所患者在于昏眊之日甚也。
叹而已。乃者春夏交。幸有南北老友齐会之约。自汶亭而始。继而有良洞文会。仍复设玉山之会而罢。盖前后殆数旬。汶亭玉院之席。则上舍族父亦与焉。是固暮境不易得之事。而但归后寥寂。亦复如前。前头炎节且迫。兀然孤坐。只作苍蝇之伴也。示喻止渊藁评骘。可见尊看文字眼目。迥出等夷。至于推借拙构。则何其爽实之甚也。岂以相爱之至。不知其恶而然耶。每于孤寂中。想执事该博之识颖锐之见。思欲合席讨论。起此衰懒。而远莫之遂。只切怅叹。一番游历仙庄。以及横溪诸胜处。追寻先辈遗迹。乃是宿昔之愿。而顾今年迫桑榆。气力垂尽。且贵中人事倏尔沧桑。便有不忍过西州之意。以是年来此愿。又付之先天者久矣。今执事之示。如是勤挚。反而思之。有如吾执事为之主而与之盘礴。则亦何间于夙世同志之相追也。窃欲以秋末枫菊之辰。为遂此愿。而但老者事。虽时月之近。亦不可指的预期。是则当付之造物者处分也。族弟道叔行录。自是不获辞者。今执事之言又如是。当拔例图之。而所患者在于昏眊之日甚也。答曹庆玉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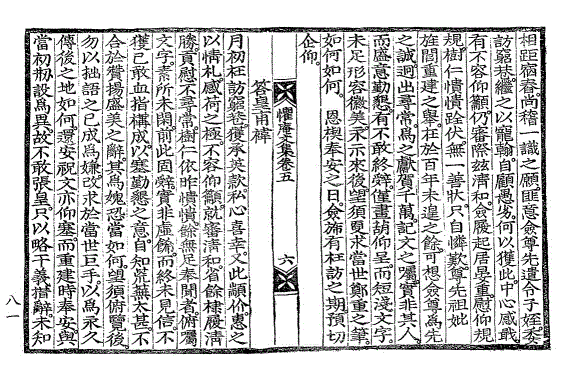 相距宿舂。尚稽一识之愿。匪意佥尊先遣令子侄。委访穷巷。继之以宠翰。自顾愚劣。何以获此。中心感戢。有不容仰吁。仍审际玆清和。佥履起居晏重。慰仰规规。树仁愦愦跧伏。无一善状。只自怜叹。尊先祖妣 旌闾重建之举。在于百年未遑之馀。可想佥尊为先之诚。迥出寻常。为之献贺千万。记文之嘱。实非其人。而盛意勤恳。有不敢终辞。仅画葫仰呈。而短浅文字。未足形容徽美。永示来后。望须更求当世郑重之笔。如何如何。 恩楔奉安之日。佥旆有枉访之期。预切企仰。
相距宿舂。尚稽一识之愿。匪意佥尊先遣令子侄。委访穷巷。继之以宠翰。自顾愚劣。何以获此。中心感戢。有不容仰吁。仍审际玆清和。佥履起居晏重。慰仰规规。树仁愦愦跧伏。无一善状。只自怜叹。尊先祖妣 旌闾重建之举。在于百年未遑之馀。可想佥尊为先之诚。迥出寻常。为之献贺千万。记文之嘱。实非其人。而盛意勤恳。有不敢终辞。仅画葫仰呈。而短浅文字。未足形容徽美。永示来后。望须更求当世郑重之笔。如何如何。 恩楔奉安之日。佥旆有枉访之期。预切企仰。答皇甫袆
月初枉访穷巷。获承英款。私心喜幸。又此颛价。惠之以情札。感荷之极。不容仰吁。就审清和。省馀棣履清胜。贡慰不寻常。树仁依昨愦愦。馀无足奉闻者。俯嘱文字。素所未闲。前此固辞。实非虚饰。而终未见信。不获已敢血指构成。以塞勤恳之意。自知荒芜太甚。不合于赞扬盛美之辞。其为愧恐当如何。望须俯览后。勿以拙语之已成为嫌。改求于当世巨手。以为永久传后之地如何。还安祝文亦仰塞。而重建时奉安。与当初刱设为异。故不敢张皇。只以略干义措辞。未知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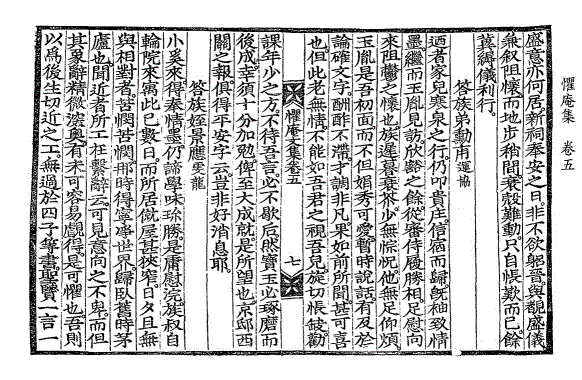 盛意亦何居。新祠奉安之日。非不欲躬晋。与睹盛仪。兼叙阻怀。而地步稍间。衰壳难动。只自怅叹而已。馀冀缛仪利行。
盛意亦何居。新祠奉安之日。非不欲躬晋。与睹盛仪。兼叙阻怀。而地步稍间。衰壳难动。只自怅叹而已。馀冀缛仪利行。答族弟勋甫(运协)
乃者家儿寒泉之行。仍叩贵庄。信宿而归。既袖致情墨。继而玉胤见访。欣豁之馀。从审侍履胜相。足慰向来阻郁之怀也。族迟暮衰苶。少无悰恍。他无足仰烦。玉胤是吾初面。而不但娟秀可爱。暂时说话。有及于论确文字。酬酢不滞。才调非凡。果如前所闻。甚可喜也。但此老无情。不能如吾君之视吾儿。旋切怅缺。劝课年少之方。不待吾言。必不歇后。然宝玉必琢磨而后成。幸须十分加勉。俾至大成就。是所望也。京邸西关之报。俱得平安字云。岂非好消息耶。
答族侄景应(雯龙)
小奚来。得奉情墨。仍谛学味珍胜。是庸慰浣。族叔自轮院来寓此已数日。而所居僦屋甚狭窄。日夕且无与相对者。苦悯苦悯。那时得宁净世界。归卧旧时茅庐也。闻近者所工在系辞云。可见意向之不卑。而但其象辞精微深奥。有未可容易觑得。是可惧也。吾则以为后生切近之工。无过于四子等书。圣贤一言一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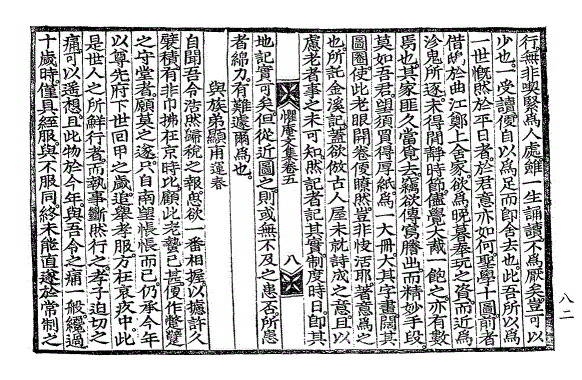 行。无非吃紧为人处。虽一生诵读。不为厌矣。岂可以少也。一受读。便自以为足而即舍去也。此吾所以为一世慨然于平日者。于君意亦如何。圣学十图。前者借䲭于曲江郑上舍家。欲为晚暮奉玩之资。而近为沴鬼所逐。未得閒静时节。尽觉大胾一饱之。亦有数焉也。其家匪久当觅去。窃欲传写誊出。而精妙手段。莫如吾君。望须买得厚纸。为一大册。大其字画。阔其图圈。使此老眼开卷便瞭然。岂非快活耶。著意为之也。所托金溪记。盖欲仿古人屋未就诗成之意。且以虑老者事之未可知。然记者记其实。制度时日。即其地记实可矣。但从近图之。则或无不及之患否。所患者绵力。有难遽尔为也。
行。无非吃紧为人处。虽一生诵读。不为厌矣。岂可以少也。一受读。便自以为足而即舍去也。此吾所以为一世慨然于平日者。于君意亦如何。圣学十图。前者借䲭于曲江郑上舍家。欲为晚暮奉玩之资。而近为沴鬼所逐。未得閒静时节。尽觉大胾一饱之。亦有数焉也。其家匪久当觅去。窃欲传写誊出。而精妙手段。莫如吾君。望须买得厚纸。为一大册。大其字画。阔其图圈。使此老眼开卷便瞭然。岂非快活耶。著意为之也。所托金溪记。盖欲仿古人屋未就诗成之意。且以虑老者事之未可知。然记者记其实。制度时日。即其地记实可矣。但从近图之。则或无不及之患否。所患者绵力。有难遽尔为也。与族弟显甫(运春)
自闻吾令浩然归税之报。思欲一番相握。以摅许久襞积。有非巾拂在京时比。顾此老蛰已甚。便作蹩躠之守堂者。愿莫之遂。只自南望怅怅而已。仍承今年以尊先府下世回甲之岁。追举孝服。方在哀疚中。此是世人之所鲜行者。而执事断然行之。孝子迫切之痛。可以遥想。且此物于今年。与吾令之痛一般。才过十岁时。仅具绖服。与不服同。终未能直遂于常制之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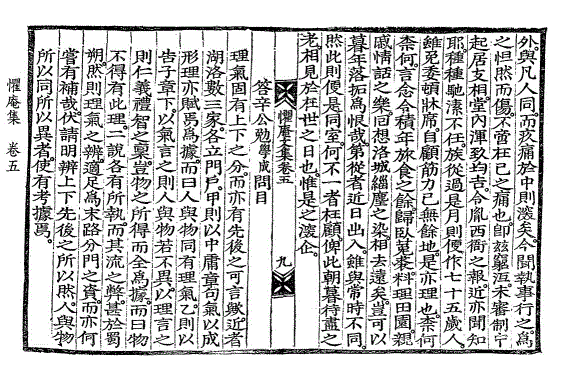 外。与凡人同。而疚痛于中则深矣。今闻执事行之。为之怛然而伤。不啻在己之痛也。即玆穷冱。未审制中起居支相。堂内浑致均吉。令胤西衙之报。近亦闻知耶。种种驰溸不任。族从过是月则便作七十五岁人。虽免委顿床席。自顾筋力已无馀地。是亦理也。柰何柰何。言念令积年旅食之馀。归卧菟裘。料理田园。亲戚情话之乐。回想洛城缁尘之染。相去远矣。岂可以暮年落拓为恨哉。第从者近日出入。虽与常时不同。然此则便是同室。何不一者枉顾。俾此朝暮待尽之老。相见于在世之日也。惟是之深企。
外。与凡人同。而疚痛于中则深矣。今闻执事行之。为之怛然而伤。不啻在己之痛也。即玆穷冱。未审制中起居支相。堂内浑致均吉。令胤西衙之报。近亦闻知耶。种种驰溸不任。族从过是月则便作七十五岁人。虽免委顿床席。自顾筋力已无馀地。是亦理也。柰何柰何。言念令积年旅食之馀。归卧菟裘。料理田园。亲戚情话之乐。回想洛城缁尘之染。相去远矣。岂可以暮年落拓为恨哉。第从者近日出入。虽与常时不同。然此则便是同室。何不一者枉顾。俾此朝暮待尽之老。相见于在世之日也。惟是之深企。答辛公勉(学成)问目
理气固有上下之分。而亦有先后之可言欤。近者湖洛数三家。各立门户。甲则以中庸章句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为据。而曰人与物同有理气。乙则以告子章下。以气言之则人与物若不异。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为据。而曰物不得有此理。二说各有所执。而其流之弊。甚于蜀朔。然则理气之辨。适足为末路分门之资。而亦何尝有补哉。伏请明辨上下先后之所以然。人与物所以同所以异者。使有考据焉。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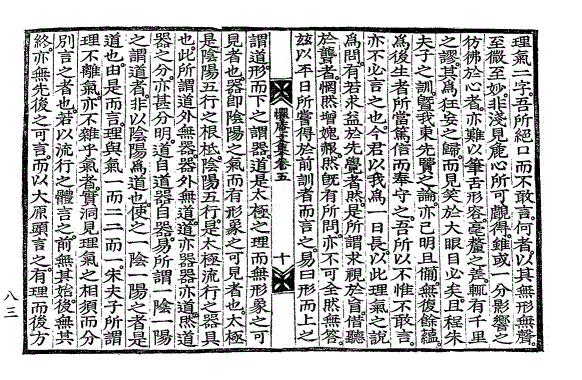 理气二字。吾所绝口而不敢言。何者。以其无形无声。至微至妙。非浅见粗心所可觑得。虽或一分影响之彷佛于心者。亦难以笔舌形容。毫釐之差。辄有千里之谬。其为狂妄之归。而见笑于大眼目必矣。且程朱夫子之训。暨我东先贤之论。亦已明且备。无复馀蕴。为后生者所当笃信而奉守之。吾所以不惟不敢言。亦不必言之也。今君以我为一日长。以此理气之说为问。有若求益于先觉者然。是所谓求视于盲。借听于聋者。惘然增愧赧。然既有所问。亦不可全然无答。玆以平日所尝得于前训者而言之。易曰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道是太极之理而无形象之可见者也。器即阴阳之气而有形象之可见者也。太极是阴阳五行之根柢。阴阳五行。是太极流行之器具也。此所谓道外无器。器外无道。道亦器器亦道。然道器之分。亦甚分明。道自道器自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非以阴阳为道也。使之一阴一阳之者是道也。由是而言。理与气一而二二而一。朱夫子所谓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者。实洞见理气之相须而分别言之者也。若以流行之体言之。前无其始。后无其终。亦无先后之可言。而以大原头言之。有理而后方
理气二字。吾所绝口而不敢言。何者。以其无形无声。至微至妙。非浅见粗心所可觑得。虽或一分影响之彷佛于心者。亦难以笔舌形容。毫釐之差。辄有千里之谬。其为狂妄之归。而见笑于大眼目必矣。且程朱夫子之训。暨我东先贤之论。亦已明且备。无复馀蕴。为后生者所当笃信而奉守之。吾所以不惟不敢言。亦不必言之也。今君以我为一日长。以此理气之说为问。有若求益于先觉者然。是所谓求视于盲。借听于聋者。惘然增愧赧。然既有所问。亦不可全然无答。玆以平日所尝得于前训者而言之。易曰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道是太极之理而无形象之可见者也。器即阴阳之气而有形象之可见者也。太极是阴阳五行之根柢。阴阳五行。是太极流行之器具也。此所谓道外无器。器外无道。道亦器器亦道。然道器之分。亦甚分明。道自道器自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非以阴阳为道也。使之一阴一阳之者是道也。由是而言。理与气一而二二而一。朱夫子所谓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者。实洞见理气之相须而分别言之者也。若以流行之体言之。前无其始。后无其终。亦无先后之可言。而以大原头言之。有理而后方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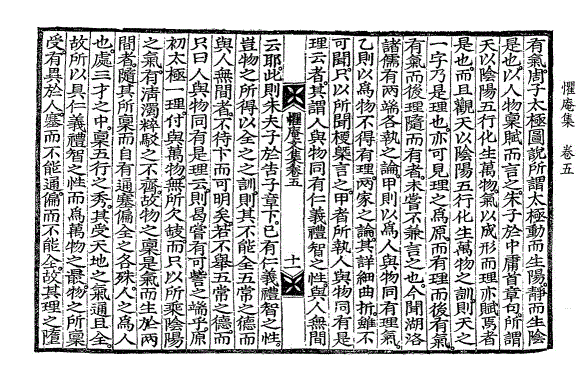 有气。周子太极图说所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是也。以人物禀赋而言之。朱子于中庸首章句。所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者是也。而且观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之训。则天之一字乃是理也。亦可见理之为原。而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理随而有者。未尝不兼言之也。今闻湖洛诸儒有两端各执之论。甲则以为人与物同有理气。乙则以为物不得有理。两家之论。其详细曲折。虽不可闻。只以所闻梗槩言之。甲者所执人与物同有是理云者。其谓人与物同有仁义礼智之性。与人无间云耶。此则朱夫子于告子章下。已有仁义礼智之性。岂物之所得以全之之训。则其不能全五常之德而与人无间者。不待卞而可明矣。若不举五常之德。而只曰人与物同有是理云。则曷尝有可訾之端乎。原初太极一理。付与万物。无所欠缺。而只以所乘阴阳之气。有清浊粹驳之不齐。故物之禀是气而生于两间者。随其所禀而自有通塞偏全之各殊。人之为人也。处三才之中。禀五行之秀。其受天地之气通且全。故所以具仁义礼智之性而为万物之最。物之所禀受。有异于人。塞而不能通。偏而不能全。故其理之堕
有气。周子太极图说所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是也。以人物禀赋而言之。朱子于中庸首章句。所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者是也。而且观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之训。则天之一字乃是理也。亦可见理之为原。而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理随而有者。未尝不兼言之也。今闻湖洛诸儒有两端各执之论。甲则以为人与物同有理气。乙则以为物不得有理。两家之论。其详细曲折。虽不可闻。只以所闻梗槩言之。甲者所执人与物同有是理云者。其谓人与物同有仁义礼智之性。与人无间云耶。此则朱夫子于告子章下。已有仁义礼智之性。岂物之所得以全之之训。则其不能全五常之德而与人无间者。不待卞而可明矣。若不举五常之德。而只曰人与物同有是理云。则曷尝有可訾之端乎。原初太极一理。付与万物。无所欠缺。而只以所乘阴阳之气。有清浊粹驳之不齐。故物之禀是气而生于两间者。随其所禀而自有通塞偏全之各殊。人之为人也。处三才之中。禀五行之秀。其受天地之气通且全。故所以具仁义礼智之性而为万物之最。物之所禀受。有异于人。塞而不能通。偏而不能全。故其理之堕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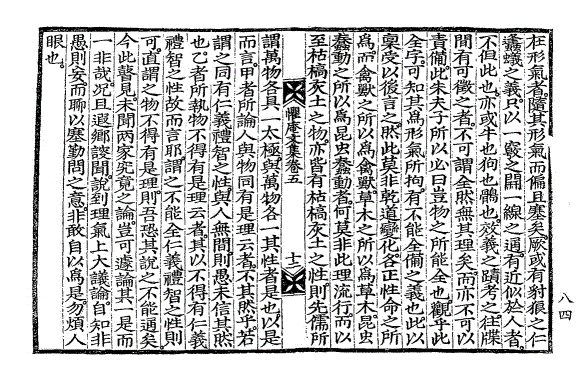 在形气者。随其形气而偏且塞矣。厥或有豺狼之仁蜂蚁之义。只以一窍之开一线之通。有近似于人者。不但此也。亦或牛也狗也鹘也。效义之迹考之。往牒间有可徵之者。不可谓全然无其理矣。而亦不可以责备。此朱夫子所以必曰岂物之所能全也。观乎此全字。可知其为形气所拘。有不能全备之义也。此以禀受以后言之。然此莫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所为。而禽兽之所以为禽兽。草木之所以为草木。昆虫蠢动之所以为昆虫蠢动者。何莫非此理流行。而以至枯槁灰土之物。亦皆有枯槁灰土之性。则先儒所谓万物各具一太极。与万物各一其性者是也。以是而言。甲者所论人与物同有是理云者。不其然乎。若谓之同有仁义礼智之性。与人无间。则愚未信其然也。乙者所执物不得有是理云者。其以不得有仁义礼智之性故而言耶。谓之不能全仁义礼智之性则可。直谓之物不得有是理。则吾恐其说之不能通矣。今此瞽见。未闻两家究竟之论。岂可遽论其一是而一非哉。况且遐乡謏闻。说到理气上大议论。自知非愚则妄。而聊以塞勤问之意。非敢自以为是。勿烦人眼也。
在形气者。随其形气而偏且塞矣。厥或有豺狼之仁蜂蚁之义。只以一窍之开一线之通。有近似于人者。不但此也。亦或牛也狗也鹘也。效义之迹考之。往牒间有可徵之者。不可谓全然无其理矣。而亦不可以责备。此朱夫子所以必曰岂物之所能全也。观乎此全字。可知其为形气所拘。有不能全备之义也。此以禀受以后言之。然此莫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所为。而禽兽之所以为禽兽。草木之所以为草木。昆虫蠢动之所以为昆虫蠢动者。何莫非此理流行。而以至枯槁灰土之物。亦皆有枯槁灰土之性。则先儒所谓万物各具一太极。与万物各一其性者是也。以是而言。甲者所论人与物同有是理云者。不其然乎。若谓之同有仁义礼智之性。与人无间。则愚未信其然也。乙者所执物不得有是理云者。其以不得有仁义礼智之性故而言耶。谓之不能全仁义礼智之性则可。直谓之物不得有是理。则吾恐其说之不能通矣。今此瞽见。未闻两家究竟之论。岂可遽论其一是而一非哉。况且遐乡謏闻。说到理气上大议论。自知非愚则妄。而聊以塞勤问之意。非敢自以为是。勿烦人眼也。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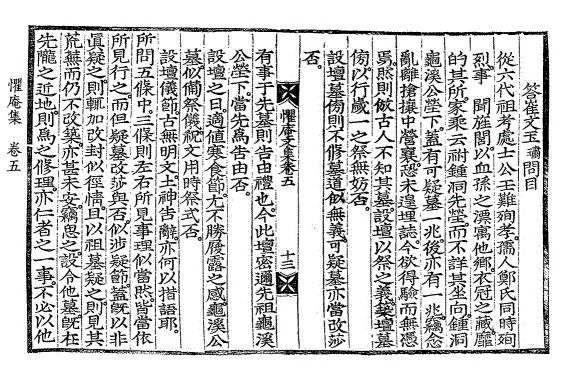 答崔文玉(璛)问目
答崔文玉(璛)问目从六代祖考处士公壬难殉孝。孺人郑氏同时殉烈。事 闻旌闾。以血孙之漂寓他乡。衣冠之藏。靡的其所。家乘云祔钟洞先茔。而不详其坐向。钟洞龟溪公茔下。盖有可疑墓一兆。后亦有一兆。窃念乱离抢攘中营襄。恐未遑埋志。今欲得验而无凭焉。然则仿古人不知其墓。设坛以祭之义。筑坛墓傍。以行岁一之祭无妨否。
设坛墓傍则不修墓道似无义。可疑墓亦当改莎否。
有事于先墓则告由礼也。今此坛密迩先祖龟溪公茔下。当先为告由否。
设坛之日。适值寒食节。尤不胜履露之感。龟溪公墓。似备祭仪。祝文用时祭式否。
设坛仪节。古无明文。土神告辞。亦何以措语耶。
所问五条中。三条则左右所见事理似当然。皆当依所见行之。而但疑墓改莎与否。似涉疑节。盖既以非真疑之。则辄加改封似径情。且以祖墓疑之。则见其荒芜而仍不改筑。亦甚未安。窃思之。设令他墓。既在先陇之近地。则为之修理。亦仁者之一事。不必以他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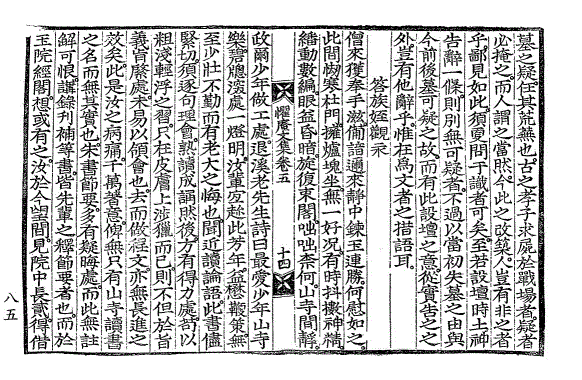 墓之疑。任其荒芜也。古之孝子求尸于战场者。疑者必掩之。而人谓之当然。今此之改筑。人岂有非之者乎。鄙见如此。须更问于识者可矣。至若设坛时土神告辞一条。则别无可疑者。不过以当初失墓之由与今前后墓可疑之故。而有此设坛之意。从实告之之外。岂有他辞乎。惟在为文者之措语耳。
墓之疑。任其荒芜也。古之孝子求尸于战场者。疑者必掩之。而人谓之当然。今此之改筑。人岂有非之者乎。鄙见如此。须更问于识者可矣。至若设坛时土神告辞一条。则别无可疑者。不过以当初失墓之由与今前后墓可疑之故。而有此设坛之意。从实告之之外。岂有他辞乎。惟在为文者之措语耳。答族侄观永
僧来获奉手滋。备谙迩来静中鍊玉连胜。何慰如之。此间怯寒杜门。拥炉块坐。无一好况。有时抖擞神精。翻动数编。眼益昏暗。旋复束阁。咄咄柰何。山寺间静。政尔少年做工处。退溪老先生诗曰最爱少年山寺乐。碧窗深处一灯明。汝辈宜趁此芳年。益懋鞭策。无至少壮不勤而有老大之悔也。闻近读论语。此书尽紧切。须逐句理会。熟读成诵然后。方有得力处。苟以粗浅轻浮之习。只在皮肤上涉猎而已。则不但于旨义肯綮处。未易以领会也。去而做程文。亦无长进之效矣。此是汝之病痛。千万著意。俾无只有山寺读书之名而无其实也。朱书节要。多有疑晦处。而此无注解可恨。讲录刊补等书。皆先辈之释节要者也。而于玉院经阁。想或有之。汝于今望间。见院中长贰。得借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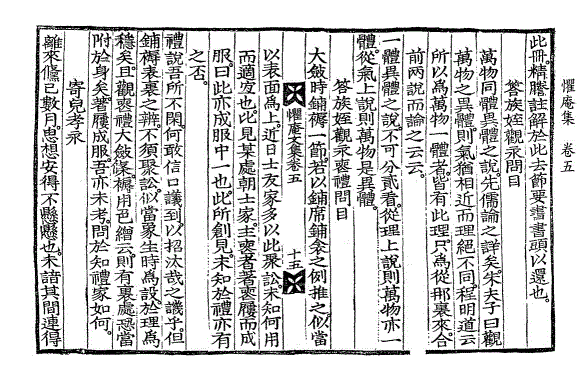 此册。精誊注解于此去节要书书头以还也。
此册。精誊注解于此去节要书书头以还也。答族侄观永问目
万物同体异体之说。先儒论之详矣。朱夫子曰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程明道云所以为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合前两说而论之云云。
一体异体之说。不可分贰看。从理上说则万物亦一体。从气上说则万物是异体。
答族侄观永丧礼问目
大敛时铺褥一节。若以铺席铺衾之例推之。似当以表面为上。近日士友家多以此聚讼。未知何用而适宜也。比见某处朝士家。主丧者著丧屦而成服。曰此亦成服中一也。此所创见。未知于礼亦有之否。
礼说吾所不闲。何敢信口议到。以招汰哉之讥乎。但铺褥表里之辨。不须聚讼。似当象生时为设。于理为稳矣。且观丧礼大敛条。褥用色缯云。则有里处恐当附于身矣。著屦成服。吾亦未考。问于知礼家如何。
寄儿孝永
离来倏已数月。思想安得不悬悬也。未谙其间连得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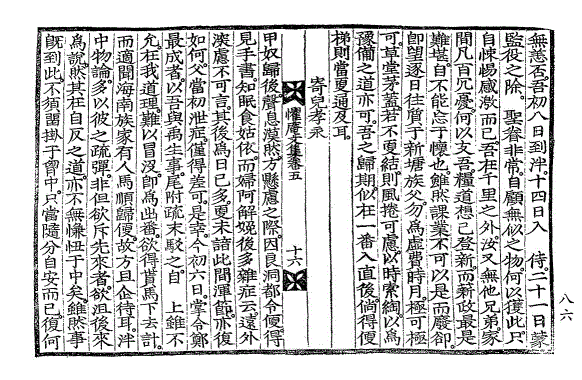 无恙否。吾初八日到泮。十四日入 侍。二十一日蒙监役之除。 圣眷非常。自顾无似之物。何以获此。只自悚惕感激而已。吾在千里之外。汝又无他兄弟。家间凡百冗忧。何以支吾。粮道想已登新。而薪政最是难堪。自不能忘于怀也。虽然课业不可以是而废却。即望逐日往质于新塘族父。勿为虚费时月。极可极可。草堂茅盖。若不更结。则风捲可虑。以时索绹。以为豫备之道亦可。吾之归期。似在一番入直后。倘得便梯则当更通及耳。
无恙否。吾初八日到泮。十四日入 侍。二十一日蒙监役之除。 圣眷非常。自顾无似之物。何以获此。只自悚惕感激而已。吾在千里之外。汝又无他兄弟。家间凡百冗忧。何以支吾。粮道想已登新。而薪政最是难堪。自不能忘于怀也。虽然课业不可以是而废却。即望逐日往质于新塘族父。勿为虚费时月。极可极可。草堂茅盖。若不更结。则风捲可虑。以时索绹。以为豫备之道亦可。吾之归期。似在一番入直后。倘得便梯则当更通及耳。寄儿孝永
甲奴归后。声息漠然。方悬虑之际。因良洞都令便。得见手书。知眠食姑依。而妇阿解娩后多杂症云。远外深虑不可言。其后为日已多。更未谙此间浑节。亦复如何。父当初泄症。仅得差可。是幸。今初六日。掌令郑最成者。以吾与禹生事。尾附疏末驳之。自 上虽不允。在我道理。难以冒没。即为出番。欲得贳马下去计。而适闻海南族家有人马顺归便。故方且企待耳。泮中物论。多以彼之疏弹。非但欲斥先来者。欲沮后来为说。然其在自反之道。亦不无慊忸于中矣。虽然事既到此。不须留挂于胸中。只当随分自安而已。复何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7H 页
 怨尤乎人哉。此书之到。若在于甲奴未发之前。则多有省弊之端。而此何可必也。
怨尤乎人哉。此书之到。若在于甲奴未发之前。则多有省弊之端。而此何可必也。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杂著
自警说
昔夏侯胜,黄霸在狱中。霸从胜受尚书。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噫。霸之此言。足以为后生困于贫窭。不能为学者之戒也。夫人之患难困厄。莫甚于缧绁拘幽之中。使常人处此。孰不曰此非讲学之时。姑待平閒无事之时。不为晚也。而斯人也乃独指死为期。不以患难困厄废业。而孜孜焉若是。则其笃实向学之意。为如何哉。世之安乐无事。懒惰不学者。已无可论。而间有有志为学者。𨓏𨓏以贫窭废业者。夫贫窭之迫人困人虽已甚。然其视缧绁拘幽之苦。又孰甚也。彼犹不以缧绁之苦而废业。则此以贫窭困穷之不胜而虚度日月者。乌乎其可也。是诚黄子之罪人也。顾余非无向学之志。而恐有以贫窭中废者。故为之说以自警云。
杀龟放龟说
吾适病疽。方云龟能已之。人有猎其二至。或曰龟为物灵。恩与雠有报。不可杀。又其生亦血类。又何忍杀。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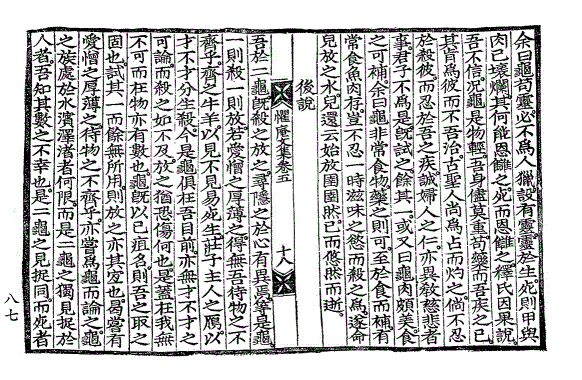 余曰龟苟灵。必不为人猎。设有灵。灵于生。死则甲与肉已坏烂。其何能恩雠之。死而恩雠之。释氏因果说。吾不信。况龟是物轻。吾身尽莫重。苟药而吾疾之已。其肯为彼而不吾治。古圣人尚为占而灼之。倘不忍于杀彼。而忍于吾之疾。诚妇人之仁。亦异教慈悲者事。君子不为是。既试之。馀其一。或又曰龟肉颇美。食之可补。余曰龟非常食物。药之则可。至于食而补。有常食鱼肉存。岂不忍一时滋味之欲而杀之为。遂命儿放之水。儿还云始放圉圉然。已而悠然而逝。
余曰龟苟灵。必不为人猎。设有灵。灵于生。死则甲与肉已坏烂。其何能恩雠之。死而恩雠之。释氏因果说。吾不信。况龟是物轻。吾身尽莫重。苟药而吾疾之已。其肯为彼而不吾治。古圣人尚为占而灼之。倘不忍于杀彼。而忍于吾之疾。诚妇人之仁。亦异教慈悲者事。君子不为是。既试之。馀其一。或又曰龟肉颇美。食之可补。余曰龟非常食物。药之则可。至于食而补。有常食鱼肉存。岂不忍一时滋味之欲而杀之为。遂命儿放之水。儿还云始放圉圉然。已而悠然而逝。后说
吾于二龟。既杀之放之。寻隐之于心有异焉。等是龟。一则杀一则放。若爱憎之厚薄之。得无吾待物之不齐乎。齐之牛羊。以见不见易死生。庄子主人之雁。以才不才分生杀。今是龟俱在吾目前。亦无才不才之可论。而杀之如不及。放之犹恐伤何也。是盖在我无不可而在物亦有数也。龟既以已疽名。则吾之取之固也。试其一而馀无所用。则放之亦其宜也。曷尝有爱憎之厚薄之。待物之不齐乎。亦尝为龟而论之。龟之族处于水滨泽渚者何限。而是二龟之独见捉于人者。吾知其数之不幸也。是二龟之见捉同。而死者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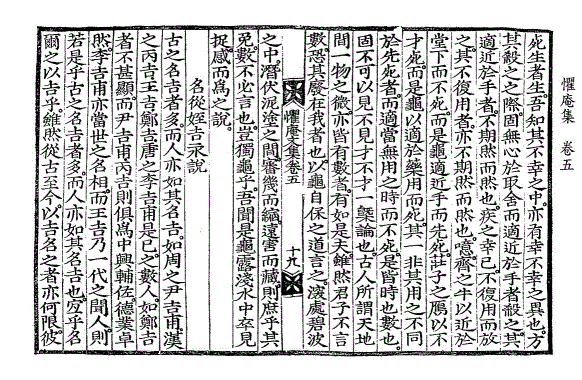 死生者生。吾知其不幸之中。亦有幸不幸之异也。方其杀之之际。固无心于取舍而适近于手者杀之。其适近于手者。不期然而然也。疾之幸已。不复用而放之。其不复用者。亦不期然而然也。噫。齐之牛以近于堂下而不死。而是龟适近手而先死。庄子之雁以不才死。而是龟以适于药用而死。其一非其用之不同于先死者。而适当无用之时而不死。是皆时也数也。固不可以见不见才不才一槩论也。古人所谓天地间一物之微。亦皆有数者。有如是夫。虽然君子不言数。恐其废在我者也。以龟自保之道言之。深处碧波之中。潜伏泥涂之间。审几而缩。远害而藏。则庶乎其免。数不必言也。岂独龟乎。吾闻是龟露浅水中卒见捉。感而为之说。
死生者生。吾知其不幸之中。亦有幸不幸之异也。方其杀之之际。固无心于取舍而适近于手者杀之。其适近于手者。不期然而然也。疾之幸已。不复用而放之。其不复用者。亦不期然而然也。噫。齐之牛以近于堂下而不死。而是龟适近手而先死。庄子之雁以不才死。而是龟以适于药用而死。其一非其用之不同于先死者。而适当无用之时而不死。是皆时也数也。固不可以见不见才不才一槩论也。古人所谓天地间一物之微。亦皆有数者。有如是夫。虽然君子不言数。恐其废在我者也。以龟自保之道言之。深处碧波之中。潜伏泥涂之间。审几而缩。远害而藏。则庶乎其免。数不必言也。岂独龟乎。吾闻是龟露浅水中卒见捉。感而为之说。名从侄吉永说
古之名吉者多。而人亦如其名吉。如周之尹吉甫,汉之丙吉,王吉,郑吉,唐之李吉甫是已。之数人。如郑吉者不甚显。而尹吉甫,丙吉则俱为中兴辅佐。德业卓然。李吉甫亦当世之名相。而王吉乃一代之闻人。则若是乎古之名吉者多。而人亦如其名吉也。宜乎名尔之以吉乎。虽然从古至今。以吉名之者亦何限。彼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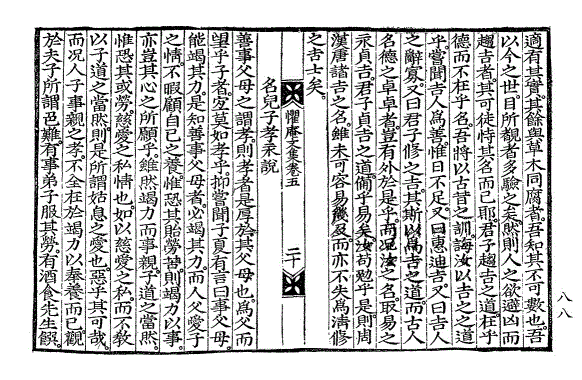 适有其实。其馀与草木同腐者。吾知其不可数也。吾以今之世。目所睹者多验之矣。然则人之欲避凶而趋吉者。其可徒恃其名而已耶。君子趋吉之道。在乎德而不在乎名。吾将以古昔之训。诲汝以吉之之道乎。尝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又曰惠迪吉。又曰吉人之辞寡。又曰君子修之吉。其斯以为吉之道。而古人名德之卓卓者。岂有外于是乎。而况汝之名。取易之永贞吉。君子贞吉之道。备乎易矣。汝苟勉乎是。则周汉唐诸吉之名。虽未可容易几及。而亦不失为清修之吉士矣。
适有其实。其馀与草木同腐者。吾知其不可数也。吾以今之世。目所睹者多验之矣。然则人之欲避凶而趋吉者。其可徒恃其名而已耶。君子趋吉之道。在乎德而不在乎名。吾将以古昔之训。诲汝以吉之之道乎。尝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又曰惠迪吉。又曰吉人之辞寡。又曰君子修之吉。其斯以为吉之道。而古人名德之卓卓者。岂有外于是乎。而况汝之名。取易之永贞吉。君子贞吉之道。备乎易矣。汝苟勉乎是。则周汉唐诸吉之名。虽未可容易几及。而亦不失为清修之吉士矣。名儿子孝永说
善事父母之谓孝。则孝者是厚于其父母也。为父而望乎子者。宜莫如孝乎。抑尝闻子夏有言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是知善事父母者。必竭其力。而人父爱子之情。不暇顾自己之养。惟恐其贻劳苦。则竭力以事。亦岂其心之所愿乎。虽然竭力而事亲。子道之当然。惟恐其或劳。慈爱之私情也。如以慈爱之私。而不教以子道之当然。则是所谓姑息之爱也。恶乎其可哉。而况人子事亲之孝。不全在于竭力以奉养而已。观于夫子所谓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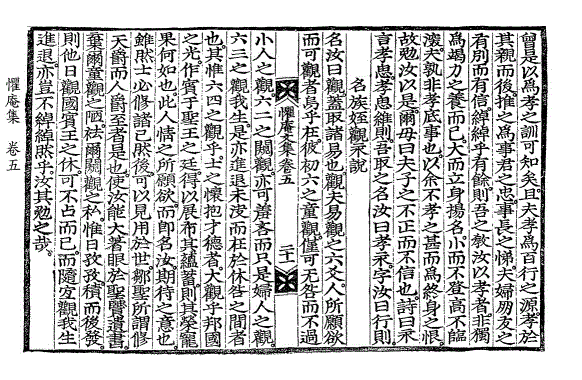 曾是以为孝之训可知矣。且夫孝为百行之源。孝于其亲而后。推之为事君之忠。事长之悌。夫妇朋友之有别而有信。绰绰乎有馀。则吾之教汝以孝者。非独为竭力之养而已。大而立身扬名。小而不登高不临深。夫孰非孝底事也。以余不孝之甚而为终身之恨。故勉汝以是。尔母曰夫子之不正而不信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吾取之名汝曰孝永。字汝曰行则。
曾是以为孝之训可知矣。且夫孝为百行之源。孝于其亲而后。推之为事君之忠。事长之悌。夫妇朋友之有别而有信。绰绰乎有馀。则吾之教汝以孝者。非独为竭力之养而已。大而立身扬名。小而不登高不临深。夫孰非孝底事也。以余不孝之甚而为终身之恨。故勉汝以是。尔母曰夫子之不正而不信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吾取之名汝曰孝永。字汝曰行则。名族侄观永说
名汝曰观。盖取诸易也。观夫易观之六爻。人所愿欲而可观者乌乎在。彼初六之童观。仅可无咎而不过小人之观。六二之窥观。亦可羞吝而只是妇人之观。六三之观我生。是亦进退未决而在于休咎之间者也。其惟六四之观乎。士之怀抱才德者。大观乎邦国之光。作宾于圣王之廷。得以展布其蕴蓄。则其荣宠果何如也。此人情之所愿欲。而即名汝。期待之意也。虽然士必修诸己然后。可以见用于世。邹圣所谓修天爵而人爵至者是也。使汝能大著眼于圣贤遗书。弃尔童观之陋。祛尔窥观之私。惟日孜孜。积而后发。则他日观国宾王之休。可不占而已。而随宜观我生进退。亦岂不绰绰然乎。汝其勉之哉。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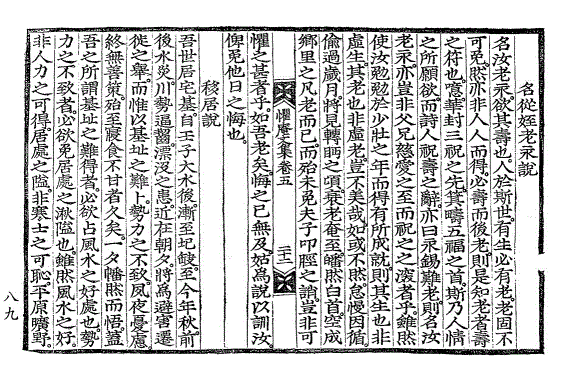 名从侄老永说
名从侄老永说名汝老永。欲其寿也。人于斯世。有生必有老。老固不可免。然亦非人人而得。必寿而后老。则是知老者寿之符也。噫。华封三祝之先。箕畴五福之首。斯乃人情之所愿欲。而诗人祝寿之辞。亦曰永锡难老。则名汝老永。亦岂非父兄慈爱之至而祝之之深者乎。虽然使汝勉勉于少壮之年而得有所成就。则其生也非虚生。其老也非虚老。岂不美哉。如或不然。怠慢因循。偷过岁月。将见转眄之顷。衰老奄至。皤然白首。空成乡里之凡老而已。而殆未免夫子叩胫之诮。岂非可惧之甚者乎。如吾老矣。悔之已无及。姑为说以训汝。俾免他日之悔也。
移居说
吾世居宅基。自壬子大水后。渐至圮缺。至今年秋。前后水灾。川势逼齧。漂没之患。近在朝夕。将为避害迁徙之举。而惟以基址之难卜。势力之不致。夙夜忧虑。终无善策。殆至寝食不甘者久矣。一夕幡然而悟。盖吾之所谓基址之难得者。必欲占风水之好处也。势力之不致者。必欲免居处之湫隘也。虽然风水之好。非人力之可得。居处之隘。非寒士之可耻。平原旷野。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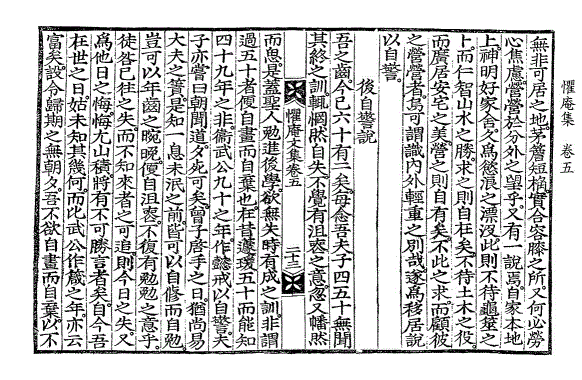 无非可居之地。茅檐短桷。实合容膝之所。又何必劳心焦虑。营营于分外之望乎。又有一说焉。自家本地上。神明好家舍。久为欲浪之漂没。此则不待龟筮之卜。而仁智山水之胜。求之则自在矣。不待土木之役。而广居安宅之美。营之则自有矣。不此之求。而顾彼之营营者。乌可谓识内外轻重之别哉。遂为移居说以自警。
无非可居之地。茅檐短桷。实合容膝之所。又何必劳心焦虑。营营于分外之望乎。又有一说焉。自家本地上。神明好家舍。久为欲浪之漂没。此则不待龟筮之卜。而仁智山水之胜。求之则自在矣。不待土木之役。而广居安宅之美。营之则自有矣。不此之求。而顾彼之营营者。乌可谓识内外轻重之别哉。遂为移居说以自警。后自警说
吾之齿。今已六十有二矣。每念吾夫子四五十无闻其终之训。辄惘然自失。不觉有沮丧之意。忽又幡然而思。是盖圣人勉进后学。欲无失时有成之训。非谓过五十者便自画而自弃也。在昔蘧瑗五十而能知四十九年之非。卫武公九十之年。作懿戒以自警。夫子亦尝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曾子启手之日。犹尚易大夫之箦。是知一息未泯之前。皆可以自修而自勉。岂可以年齿之晼晚。便自沮丧。不复有勉勉之意乎。徒咎已往之失。而不知来者之可追。则今日之失。又为他日之悔。悔尤山积。将有不可胜言者矣。自今吾在世之日。姑未知其几何。而比武公作箴之年。亦云富矣。设令归期之无朝夕。吾不欲自画而自弃。以不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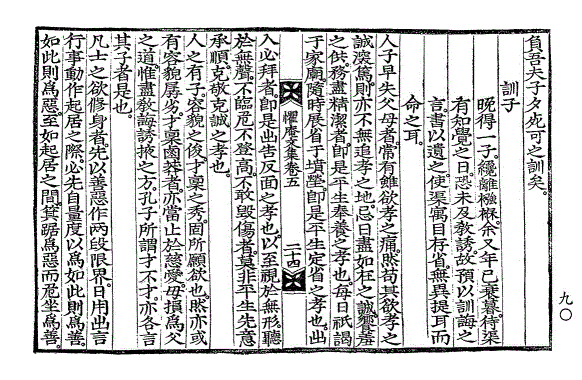 负吾夫子夕死可之训矣。
负吾夫子夕死可之训矣。训子
晚得一子。才离襁褓。余又年已衰暮。待渠有知觉之日。恐未及教诱。故预以训诲之言。书以遗之。使渠寓目存省。无异提耳而命之耳。
人子早失父母者。常有虽欲孝之痛。然苟其欲孝之诚深笃。则亦不无追孝之地。忌日尽如在之诚。飨羞之供。务尽精洁者。即是平生奉养之孝也。每日祇谒于家庙。随时展省于坟茔。即是平生定省之孝也。出入必拜者。即是出告反面之孝也。以至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不临危不登高。不敢毁伤者。莫非平生先意承顺。克敬克诚之孝也。
人之有子。容貌之俊。才禀之秀。固所愿欲也。然亦或有容貌孱劣。才禀卤莽者。亦当止于慈爱。毋损为父之道。惟尽教诲诱掖之方。孔子所谓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是也。
凡士之欲修身者。先以善恶作两段限界。日用出言行事动作起居之际。必先自量度以为如此则为善。如此则为恶。至如起居之间。箕踞为恶而危坐为善。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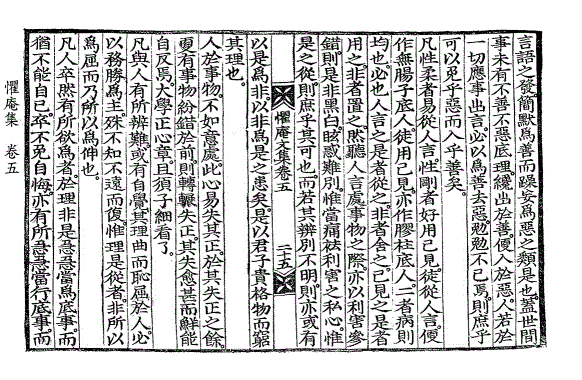 言语之发。简默为善而躁妄为恶之类是也。盖世间事未有不善不恶底理。才出于善。便入于恶。人若于一切应事出言。必以为善去恶。勉勉不已焉。则庶乎可以免乎恶而入乎善矣。
言语之发。简默为善而躁妄为恶之类是也。盖世间事未有不善不恶底理。才出于善。便入于恶。人若于一切应事出言。必以为善去恶。勉勉不已焉。则庶乎可以免乎恶而入乎善矣。凡性柔者易从人言。性刚者好用己见。徒从人言。便作无肠子底人。徒用己见。亦作胶柱底人。二者病则均也。必也人言之是者从之。非者舍之。己见之是者用之。非者置之。然听人言处事物之际。亦以利害参错。则是非黑白。眩惑难别。惟当痛袪利害之私心。惟是之从。则庶乎其可也。而若其辨别不明。则亦或有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之患矣。是以君子贵格物而穷其理也。
人于事物。不如意处。此心易失其正。于其失正之馀。更有事物纷错于前。则转辗失正。其失愈甚而鲜能自反焉。大学正心章。且须子细看了。
凡与人有所辨难。或有自觉其理曲而耻屈于人。必以务胜为主。殊不知不远而复。惟理是从者。非所以为屈而乃所以为伸也。
凡人卒然有所欲为者。于理非是急急当为底事。而犹不能自已。卒不免自悔。亦有所急急当行底事。而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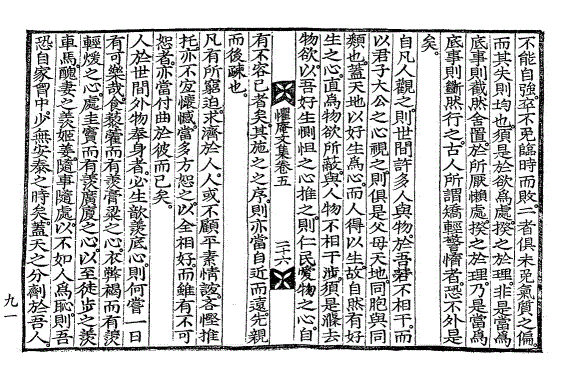 不能自强。卒不免临时而败。二者俱未免气质之偏。而其失则均也。须是于欲为处。揆之于理。非是当为底事则截然舍置。于所厌懒处。揆之于理。乃是当为底事则断然行之。古人所谓矫轻警惰者。恐不外是矣。
不能自强。卒不免临时而败。二者俱未免气质之偏。而其失则均也。须是于欲为处。揆之于理。非是当为底事则截然舍置。于所厌懒处。揆之于理。乃是当为底事则断然行之。古人所谓矫轻警惰者。恐不外是矣。自凡人观之。则世间许多人与物。于吾若不相干。而以君子大公之心视之。则俱是父母天地。同胞与同类也。盖天地以好生为心。而人得以生。故自然有好生之心。直为物欲所蔽。与人物不相干涉。须是涤去物欲。以吾好生恻怛之心推之。则仁民爱物之心。自有不容已者矣。其施之之序。则亦当自近而远。先亲而后疏也。
凡有所穷迫。求济于人。人或不顾平素情谊。吝悭推托。亦不宜怀憾。当多方恕之。以全相好。而虽有不可恕者。亦当付曲于彼而已矣。
人于世间外物奉身者。必生歆羡底心。则何尝一日有可乐哉。食藜藿而有羡膏粱之心。衣弊褐而有羡轻煖之心。处圭窦而有羡广厦之心。以至徒步之羡车马。丑妻之羡姬姜。随事随处。以不如人为耻。则吾恐自家胸中。少无安泰之时矣。盖天之分剂于吾人。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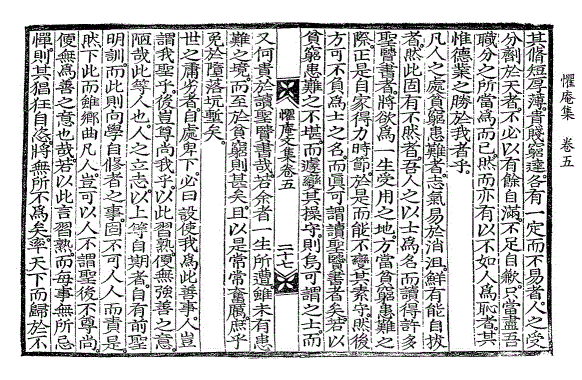 其脩短厚薄。贵贱穷达。各有一定而不易者。人之受分剂于天者。不必以有馀自满。不足自歉。只当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而已。然而亦有以不如人为耻者。其惟德业之胜于我者乎。
其脩短厚薄。贵贱穷达。各有一定而不易者。人之受分剂于天者。不必以有馀自满。不足自歉。只当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而已。然而亦有以不如人为耻者。其惟德业之胜于我者乎。凡人之处贫穷患难者。志气易于消沮。鲜有能自拔者。然此固有不然者。吾人之以士为名而读得许多圣贤书者。将欲为一生受用之地。方当贫穷患难之际。正是自家得力时节。于是而能不变其素守。然后方可不负为士之名。而真可谓读圣贤书者矣。若以贫穷患难之不堪。而遽变其操守。则乌可谓之士。而又何贵于读圣贤书哉。若余者一生所遭。虽未有患难之境。而至于贫穷则甚矣。且以是常常奋厉。庶乎免于堕落坑堑矣。
世之庸劣者。自处卑下。必曰设使我为此善事。人岂谓我圣乎。后岂尊尚我乎。以此习熟。便无强善之意。陋哉此等人也。人之立志。以上等自期者。自有前圣明训。而此则向学自修者之事。固不可人人而责是。然下此而虽乡曲凡人。岂可以人不谓圣后不尊尚。便无为善之意也哉。若以此言习熟。而每事无所忌惮。则其猖狂自恣。将无所不为矣。率天下而归于不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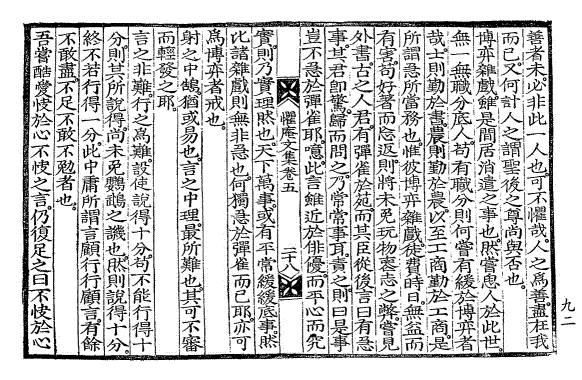 善者未。必非此一人也。可不惧哉。人之为善。尽在我而已。又何计人之谓圣后之尊尚与否也。
善者未。必非此一人也。可不惧哉。人之为善。尽在我而已。又何计人之谓圣后之尊尚与否也。博弈杂戏。虽是间居消遣之事也。然尝思人于此世。无一无职分底人。苟有职分则何尝有缓于博弈者哉。士则勤于书。农则勤于农。以至工商勤于工商。是所谓急所当务也。惟彼博弈杂戏。徒费时日。无益而有害。苟好著而忘返。则将未免玩物丧志之弊。尝见外书。古之人君。有弹雀于苑。而其臣从后言曰有急事。其君即惊。归而问之。乃常常事耳。责之。则曰是事岂不急于弹雀耶。噫。此言虽近于俳优。而平心而究实。则乃实理然也。天下万事。或有平常缓缓底事。然比诸杂戏则无非急也。何独急于弹雀而已耶。亦可为博弈者戒也。
射之中鹄。犹或易也。言之中理。最所难也。其可不审而轻发之耶。
言之非难。行之为难。设使说得十分。苟不能行得十分。则其所说得。尚未免鹦鹉之讥也。然则说得十分。终不若行得一分。此中庸所谓言顾行行顾言。有馀不敢尽。不足不敢不勉者也。
吾尝酷爱快于心不快之言。仍复足之曰不快于心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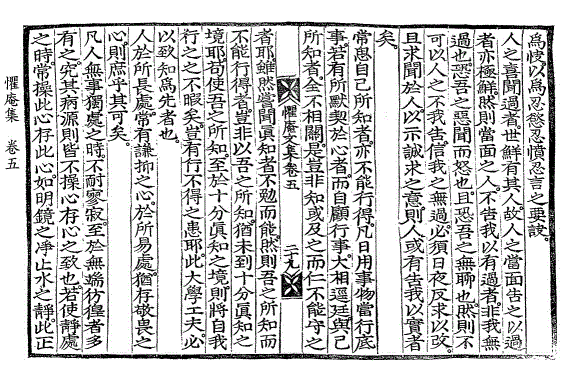 为快。以为忍欲忍愤忍言之要诀。
为快。以为忍欲忍愤忍言之要诀。人之喜闻过者。世鲜有其人。故人之当面告之以过者亦极鲜。然则当面之人。不告我以有过者。非我无过也。恐吾之恶闻而怒也。且恐吾之无聊也。然则不可以人之不我告。信我之无过。必须日夜反求以改。且求闻于人。以示诚求之意。则人或有告我以实者矣。
常思自己所知者。亦不能行得。凡日用事物当行底事。若有所默契于心者。而自顾行事。大相径廷。与己所知者。全不相关。是岂非知或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耶。虽然尝闻真知者不勉而能。然则吾之所知而不能行得者。岂非以吾之所知。犹未到十分真知之境耶。苟使吾之所知。至于十分真知之境。则将自我行之之不暇矣。岂有行不得之患耶。此大学工夫。必以致知为先者也。
人于所长处。常有谦抑之心。于所易处。犹存敬畏之心。则庶乎其可矣。
凡人无事独处之时。不耐寥寂。至于无端彷徨者多有之。究其病源则皆不操心存心之致也。若使静处之时。常操此心存此心。如明镜之净止水之静。此正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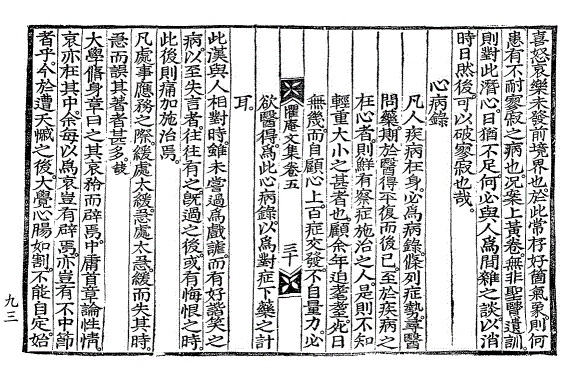 喜怒哀乐未发前境界也。于此常存好个气象。则何患有不耐寥寂之病也。况案上黄卷。无非圣贤遗训。则对此潜心。日犹不足。何必与人为间杂之谈。以消时日然后。可以破寥寂也哉。
喜怒哀乐未发前境界也。于此常存好个气象。则何患有不耐寥寂之病也。况案上黄卷。无非圣贤遗训。则对此潜心。日犹不足。何必与人为间杂之谈。以消时日然后。可以破寥寂也哉。心病录
凡人疾病在身。必为病录。条列症势。寻医问药。期于医得平复而后已。至于疾病之在心者。则鲜有察症施治之人。是则不知轻重大小之甚者也。顾余年迫耄耋。死日无几。而自顾心上。百症交发。不自量力。必欲医得。为此心病录。以为对症下药之计耳。
此汉与人相对时。虽未尝过为戏谑。而有好谐笑之病。以至失言者。往往有之。既过之后。或有悔恨之时。此后则痛加施治焉。
凡处事应务之际。缓处太缓。急处太急。缓而失其时。急而误其著者甚多。(缺)
大学脩身章曰之其哀矜而辟焉。中庸首章论性情。哀亦在其中。余每以为哀岂有辟焉。亦岂有不中节者乎。今于遭夭戚之后。大觉心肠如割。不能自定。始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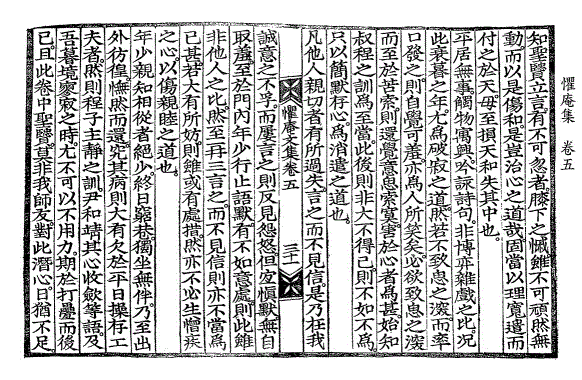 知圣贤立言。有不可忽者。膝下之戚。虽不可顽然无动。而以是伤和。是岂治心之道哉。固当以理宽遣而付之于天。毋至损天和失其中也。
知圣贤立言。有不可忽者。膝下之戚。虽不可顽然无动。而以是伤和。是岂治心之道哉。固当以理宽遣而付之于天。毋至损天和失其中也。平居无事。触物寓兴。吟咏诗句。非博弈杂戏之比。况此衰暮之年。尤为破寂之道。然若不致思之深。而率口发之。则自觉可羞。亦为人所笑矣。必欲致思之深而至于苦索。则还觉意思索寞。害于心者为甚。始知叔程之训为至当。此后则非大不得已。则不如不为。只以简默存心。为消遣之道也。
凡他人亲切者有所过失。言之而不见信。是乃在我诚意之不孚。而屡言之则反见怨怒。但宜慎默。无自取羞。至于门内年少行止语默。有不如意处。则此虽非他人之比。然至再三言之。而不见信则亦不当为已甚。若大有所妨。则虽或有处措。然亦不必生憎疾之心。以伤亲睦之道也。
年少亲知相从者绝少。终日穷巷。独坐无伴。乃至出外彷徨。怃然而还。究其病则大有欠于平日操存工夫者。然则程子主静之训。尹和靖其心收敛等语。及吾暮境寥寂之时。尤不可以不用力。期于打叠而后已。且此卷中圣贤。莫非我师友。对此潜心。日犹不足。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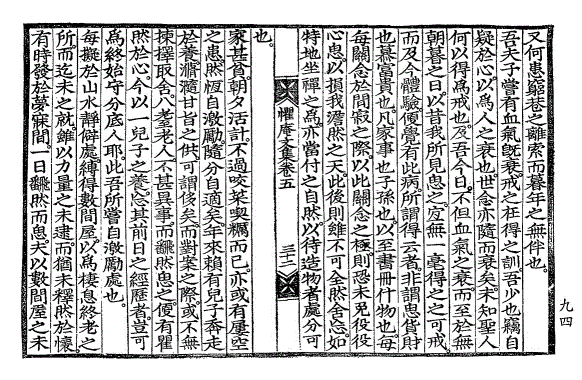 又何患穷巷之离索而暮年之无伴也。
又何患穷巷之离索而暮年之无伴也。吾夫子尝有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之训。吾少也窃自疑于心。以为人之衰也。世念亦随而衰矣。未知圣人何以得为戒也。及吾今日。不但血气之衰。而至于无朝暮之日。以昔我所见思之。宜无一毫得之之可戒。而及今体验。便觉有此病。所谓得云者。非谓思货财也慕富贵也。凡家事也子孙也。以至书册什物也。每每关念于閒寂之际。以此关念之极。则恐未免役役心思。以损我澹然之天。此后则虽不可全然舍忘。如特地坐禅之为。亦当付之自然。以待造物者处分可也。
家甚贫。朝夕活计。不过咬菜吃粝而已。亦或有屡空之患。然恒自激励。随分自适矣。年来赖有儿子奔走于养。滫瀡甘旨之供。可谓侈矣。而对案之际。或不无拣择取舍。八耋老人。不甚异事。而翻然思之。便有瞿然于心。今以一儿子之养。忘其前日之经历者。岂可为终始守分底人耶。此吾所尝自激励处也。
每拟于山水静僻处。缚得数间屋。以为栖息终老之所。而迄未之就。虽以力量之未逮。而犹未释然于怀。有时发于梦寐间。一日翻然而思。夫以数间屋之未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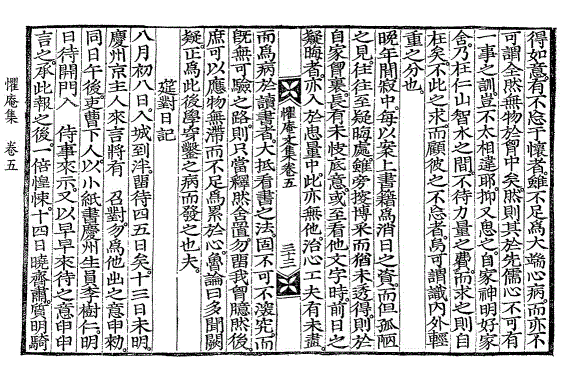 得如意。有不忘于怀者。虽不足为大端心病。而亦不可谓全然无物于胸中矣。然则其于先儒心不可有一事之训。岂不太相违耶。抑又思之。自家神明好家舍。乃在仁山智水之间。不待力量之费。而求之则自在矣。不此之求。而顾彼之不忘者。乌可谓识内外轻重之分也。
得如意。有不忘于怀者。虽不足为大端心病。而亦不可谓全然无物于胸中矣。然则其于先儒心不可有一事之训。岂不太相违耶。抑又思之。自家神明好家舍。乃在仁山智水之间。不待力量之费。而求之则自在矣。不此之求。而顾彼之不忘者。乌可谓识内外轻重之分也。晚年閒寂中。每以案上书籍为消日之资。而但孤陋之见。往往至疑晦处。虽旁搜博采而犹未透得。则于自家胸里。长有未快底意。或至看他文字时。前日之疑晦者。亦入于思量中。此亦无他。治心工夫有未尽。而为病于读书者。大抵看书之法。固不可不深究。而既无可验之路。则只当释然舍置。勿留我胸臆然后。庶可以应物无滞而不足为累于心。鲁论曰多闻阙疑。正为此后学穿凿之病而发之也夫。
筵对日记
八月初八日。入城到泮。留待四五日矣。十三日未明。庆州京主人来言将有 召对。勿为他出之意申敕。同日午后。吏曹下人。以小纸书庆州生员李树仁。明日待开门入 侍事来示。又以早早来待之意申申言之。承此报之后。一倍惶悚。十四日晓齐肃。质明骑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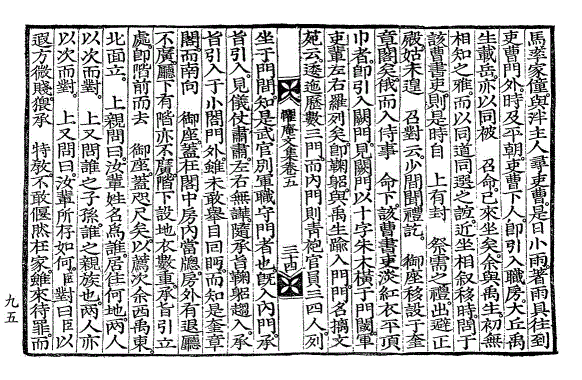 马率家僮。与泮主人寻吏曹。是日小雨。著雨具往到吏曹门外。时及平朝。吏曹下人。即引入职房。大丘禹生载岳。亦以同被 召命。已来坐矣。余与禹生。初无相知之雅。而以同道同选之谊。近坐相叙移时。问于该曹书吏。则是时自 上有封 祭需之礼。出避正殿。姑未遑 召对云。少间闻礼讫。 御座移设于奎章阁矣。俄而入侍事 命下。该曹书吏淡红衣平顶巾者。即引入阙门。见阙门以十字朱木横于门阈。军吏辈左右罗列矣。即鞠躬。与禹生踰入门。门名摛文苑云。逶迤历数三门。而内门则青袍官员三四人。列坐于门间。知是武官别军职守门者也。既入内门。承旨引入。见仪仗肃肃。左右无哗。随承旨鞠躬趋入。承旨引入于小閤门外。虽未敢举目回眄。而知是奎章阁。而南向 御座。盖在阁中房内当窗。房外有退厅不广。厅下有阶亦不广。阶下设地衣数重。承旨引立处。即阶前而去 御座。盖咫尺矣。以荐次余西禹东。北面立。 上亲问曰。汝辈姓名为谁。居住何地。两人以次而对。 上又问谁之子孙。谁之亲族也。两人亦以次而对。 上又问曰。汝辈所存如何。臣对曰臣以遐方微贱。猥承 特教。不敢偃然在家。虽来待罪。而
马率家僮。与泮主人寻吏曹。是日小雨。著雨具往到吏曹门外。时及平朝。吏曹下人。即引入职房。大丘禹生载岳。亦以同被 召命。已来坐矣。余与禹生。初无相知之雅。而以同道同选之谊。近坐相叙移时。问于该曹书吏。则是时自 上有封 祭需之礼。出避正殿。姑未遑 召对云。少间闻礼讫。 御座移设于奎章阁矣。俄而入侍事 命下。该曹书吏淡红衣平顶巾者。即引入阙门。见阙门以十字朱木横于门阈。军吏辈左右罗列矣。即鞠躬。与禹生踰入门。门名摛文苑云。逶迤历数三门。而内门则青袍官员三四人。列坐于门间。知是武官别军职守门者也。既入内门。承旨引入。见仪仗肃肃。左右无哗。随承旨鞠躬趋入。承旨引入于小閤门外。虽未敢举目回眄。而知是奎章阁。而南向 御座。盖在阁中房内当窗。房外有退厅不广。厅下有阶亦不广。阶下设地衣数重。承旨引立处。即阶前而去 御座。盖咫尺矣。以荐次余西禹东。北面立。 上亲问曰。汝辈姓名为谁。居住何地。两人以次而对。 上又问谁之子孙。谁之亲族也。两人亦以次而对。 上又问曰。汝辈所存如何。臣对曰臣以遐方微贱。猥承 特教。不敢偃然在家。虽来待罪。而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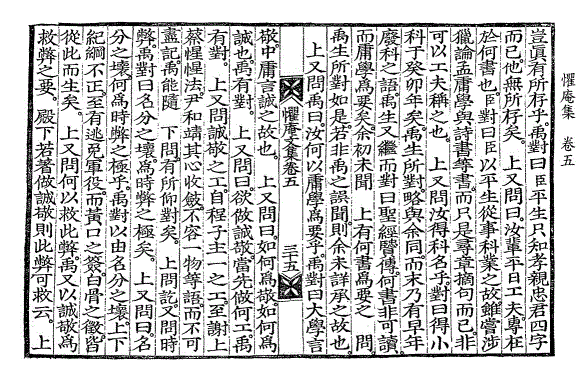 岂真有所存乎。禹对曰臣平生只知孝亲忠君四字而已。他无所存矣。 上又问曰。汝辈平日工夫。专在于何书也。臣对曰臣以平生从事科业之故。虽尝涉猎论孟庸学与诗书等书。而只是寻章摘句而已。非可以工夫称之也。 上又问汝得科名乎。对曰得小科于癸卯年矣。禹生所对。略与余同。而末乃有早年废科之语。禹生又继而对曰圣经贤传。何书非可读。而庸学为要矣。余初未闻 上有何书为要之 问。禹生所对如是。若非禹之误闻。则余未详承之故也。 上又问禹曰。汝何以庸学为要乎。禹对曰大学言敬。中庸言诚之故也。 上又问曰。如何为敬。如何为诚也。禹有对。 上又问曰。欲做诚敬。当先做何工。禹有对。 上又问诚敬之工。自程子主一之工。至谢上蔡惺惺法。尹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等语。而不可尽记。禹能随 下问。有所仰对矣。 上问讫。又问时弊。禹对曰名分之坏。为时弊之极矣。 上又问曰。名分之坏。何为时弊之极乎。禹对以由名分之坏。上下纪纲不正。至有逃免军役。而黄口之签。白骨之徵。皆从此而生矣。 上又问何以救此弊。禹又以诚敬为救弊之要。 殿下若著做诚敬则此弊可救云。 上
岂真有所存乎。禹对曰臣平生只知孝亲忠君四字而已。他无所存矣。 上又问曰。汝辈平日工夫。专在于何书也。臣对曰臣以平生从事科业之故。虽尝涉猎论孟庸学与诗书等书。而只是寻章摘句而已。非可以工夫称之也。 上又问汝得科名乎。对曰得小科于癸卯年矣。禹生所对。略与余同。而末乃有早年废科之语。禹生又继而对曰圣经贤传。何书非可读。而庸学为要矣。余初未闻 上有何书为要之 问。禹生所对如是。若非禹之误闻。则余未详承之故也。 上又问禹曰。汝何以庸学为要乎。禹对曰大学言敬。中庸言诚之故也。 上又问曰。如何为敬。如何为诚也。禹有对。 上又问曰。欲做诚敬。当先做何工。禹有对。 上又问诚敬之工。自程子主一之工。至谢上蔡惺惺法。尹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等语。而不可尽记。禹能随 下问。有所仰对矣。 上问讫。又问时弊。禹对曰名分之坏。为时弊之极矣。 上又问曰。名分之坏。何为时弊之极乎。禹对以由名分之坏。上下纪纲不正。至有逃免军役。而黄口之签。白骨之徵。皆从此而生矣。 上又问何以救此弊。禹又以诚敬为救弊之要。 殿下若著做诚敬则此弊可救云。 上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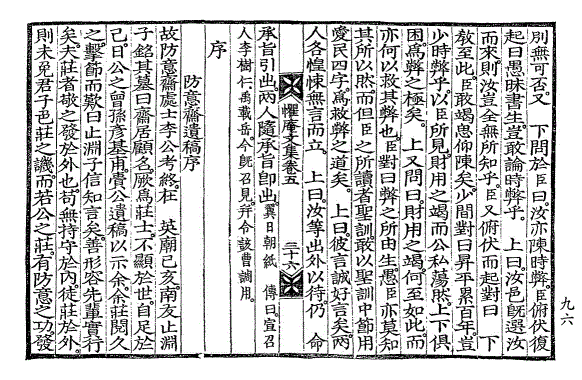 别无可否。又 下问于臣曰。汝亦陈时弊。臣俯伏复起曰愚昧书生。岂敢论时弊乎。 上曰。汝邑既选汝而来。则汝岂全无所知乎。臣又俯伏而起对曰 下教至此。臣敢竭思仰陈矣。少间对曰升平累百年。岂少时弊乎。以臣所见。财用之竭而公私荡然。上下俱困。为弊之极矣。 上又问曰。财用之竭。何至如此。而亦何以救其弊也。臣对曰弊之所由生。愚臣亦莫知其所以然。而但臣之所读者圣训。敢以圣训中节用爱民四字。为救弊之道矣。 上曰。彼言诚好言矣。两人各惶悚无言而立。 上曰。汝等出外以待。仍 命承旨引出。两人随承旨即出。(翼日朝纸 传曰。宣召人李树仁,禹载岳。今既召见。并令该曹调用。)
别无可否。又 下问于臣曰。汝亦陈时弊。臣俯伏复起曰愚昧书生。岂敢论时弊乎。 上曰。汝邑既选汝而来。则汝岂全无所知乎。臣又俯伏而起对曰 下教至此。臣敢竭思仰陈矣。少间对曰升平累百年。岂少时弊乎。以臣所见。财用之竭而公私荡然。上下俱困。为弊之极矣。 上又问曰。财用之竭。何至如此。而亦何以救其弊也。臣对曰弊之所由生。愚臣亦莫知其所以然。而但臣之所读者圣训。敢以圣训中节用爱民四字。为救弊之道矣。 上曰。彼言诚好言矣。两人各惶悚无言而立。 上曰。汝等出外以待。仍 命承旨引出。两人随承旨即出。(翼日朝纸 传曰。宣召人李树仁,禹载岳。今既召见。并令该曹调用。)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
防意斋遗稿序
故防意斋处士李公考终。在 英庙己亥。南友止渊子铭其墓曰斋居顾名。厥为庄士。不显于世。自足于己。日公之曾孙彦基甫。赍公遗稿以示余。余庄阅久之。击节而叹曰止渊子信知言矣。善形容先辈实行矣。夫庄者敬之发于外也。苟无持守于内。徒庄于外。则未免君子色庄之讥。而若公之庄。有防意之功。发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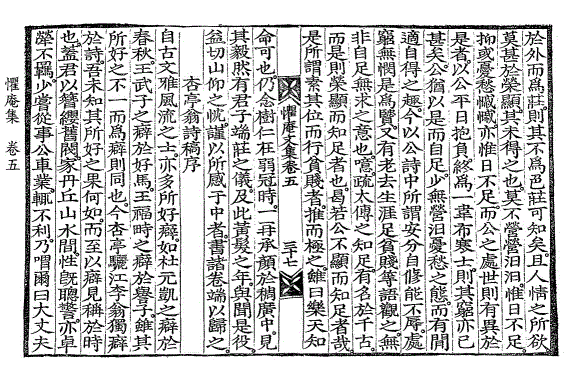 于外而为庄。则其不为色庄可知矣。且人情之所欲。莫甚于荣显。其未得之也。莫不营营汩汩。惟日不足。抑或忧愁戚戚。亦惟日不足。而公之处世则有异于是者。以公平日抱负。终为一韦布寒士。则其穷亦已甚矣。公犹以是而自足。少无营汩忧愁之态。而有閒适自得之趣。今以公诗中所谓安分自修能不辱。处穷无悯是为贤。又有老去生涯足贫贱等语观之。无非自足无求之意也。噫。疏太傅之知足。有名于千古。而是则荣显而知足者也。曷若公不显而知足者哉。是所谓素其位而行贫贱者。推而极之。虽曰乐天知命可也。仍念树仁在弱冠时。一再承颜于稠广中。见其毅然有君子端庄之仪。及此黄发之年。与闻是役。益切山仰之忱。谨以所感于中者。书诸卷端以归之。
于外而为庄。则其不为色庄可知矣。且人情之所欲。莫甚于荣显。其未得之也。莫不营营汩汩。惟日不足。抑或忧愁戚戚。亦惟日不足。而公之处世则有异于是者。以公平日抱负。终为一韦布寒士。则其穷亦已甚矣。公犹以是而自足。少无营汩忧愁之态。而有閒适自得之趣。今以公诗中所谓安分自修能不辱。处穷无悯是为贤。又有老去生涯足贫贱等语观之。无非自足无求之意也。噫。疏太傅之知足。有名于千古。而是则荣显而知足者也。曷若公不显而知足者哉。是所谓素其位而行贫贱者。推而极之。虽曰乐天知命可也。仍念树仁在弱冠时。一再承颜于稠广中。见其毅然有君子端庄之仪。及此黄发之年。与闻是役。益切山仰之忱。谨以所感于中者。书诸卷端以归之。杏亭翁诗稿序
自古文雅风流之士。亦多所好癖。如杜元凯之癖于春秋。王武子之癖于好马。王福畤之癖于誉子。虽其所好之不一而为癖则同也。今杏亭骊江李翁独癖于诗。吾未知其所好之果何如。而至以癖见称于时也。盖君以簪缨旧阀。家丹丘山水间。性既聪警。亦卓荦不羁。少尝从事公车业。辄不利。乃喟尔曰大丈夫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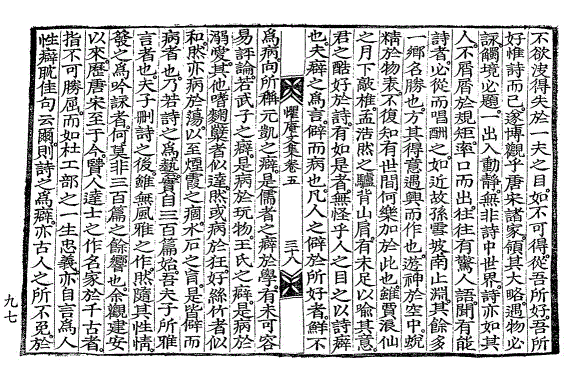 不欲决得失于一夫之目。如不可得。从吾所好。吾所好惟诗而已。遂博观乎唐宋诸家。领其大略。遇物必咏。触境必题。一出入动静。无非诗中世界。诗亦如其人。不屑屑于规矩。率口而出。往往有惊人语。闻有能诗者。必从而唱酬之。如近故孙雪坡,南止渊。其馀多一乡名胜也。方其得意遇兴而作也。游神于空中。蜕精于物表。不复知有世间何乐加于此也。虽贾浪仙之月下敲椎(一作推)。孟浩然之驴背山肩。有未足以喻其意。君之酷好于诗。有如是者。无怪乎人之目之以诗癖也。夫癖之为言。僻而病也。凡人之僻于所好者。鲜不为病。向所称元凯之癖。是儒者之癖于学。有未可容易评论。若武子之癖。是病于玩物。王氏之癖。是病于溺爱。其他嗜曲蘖者似达。然或病于狂。好丝竹者似和。然亦病于荡。以至烟霞之痼。水石之肓。是皆僻而病者也。乃若诗之为艺。实自三百篇始。吾夫子所雅言者也。夫子删诗之后。虽无风雅之作。然随其性情。发之为吟咏者。何莫非三百篇之馀响也。余观建安以来。历唐宋至于今。贤人达士之作名家于千古者。指不可胜屈。而如杜工部之一生忠义。亦自言为人性癖耽佳句云尔。则诗之为癖。亦古人之所不免。于
不欲决得失于一夫之目。如不可得。从吾所好。吾所好惟诗而已。遂博观乎唐宋诸家。领其大略。遇物必咏。触境必题。一出入动静。无非诗中世界。诗亦如其人。不屑屑于规矩。率口而出。往往有惊人语。闻有能诗者。必从而唱酬之。如近故孙雪坡,南止渊。其馀多一乡名胜也。方其得意遇兴而作也。游神于空中。蜕精于物表。不复知有世间何乐加于此也。虽贾浪仙之月下敲椎(一作推)。孟浩然之驴背山肩。有未足以喻其意。君之酷好于诗。有如是者。无怪乎人之目之以诗癖也。夫癖之为言。僻而病也。凡人之僻于所好者。鲜不为病。向所称元凯之癖。是儒者之癖于学。有未可容易评论。若武子之癖。是病于玩物。王氏之癖。是病于溺爱。其他嗜曲蘖者似达。然或病于狂。好丝竹者似和。然亦病于荡。以至烟霞之痼。水石之肓。是皆僻而病者也。乃若诗之为艺。实自三百篇始。吾夫子所雅言者也。夫子删诗之后。虽无风雅之作。然随其性情。发之为吟咏者。何莫非三百篇之馀响也。余观建安以来。历唐宋至于今。贤人达士之作名家于千古者。指不可胜屈。而如杜工部之一生忠义。亦自言为人性癖耽佳句云尔。则诗之为癖。亦古人之所不免。于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8H 页
 君独何病乎。虽然因君之所好而吾有所加勉焉。以君之才。居今之世。能自拔于流俗。啸傲散朗。以吟风弄月为乐者。岂不诚豪士哉。但君子所乐。有大于是者。以君酷好于诗者。移之于内。养吾中和之性。充乎中而发之为英华。则无是病而有是乐。又何如也。昔退陶老先生于放翁。有终诧诗狂自绝听之讥。吾敢以是艾君之癖。君其有意乎。姑书诗轴上以俟。君名之翰字乃宪。与余最相善。宅边有文杏树亭亭可爱。是为君日哦之所。仍以自号云。
君独何病乎。虽然因君之所好而吾有所加勉焉。以君之才。居今之世。能自拔于流俗。啸傲散朗。以吟风弄月为乐者。岂不诚豪士哉。但君子所乐。有大于是者。以君酷好于诗者。移之于内。养吾中和之性。充乎中而发之为英华。则无是病而有是乐。又何如也。昔退陶老先生于放翁。有终诧诗狂自绝听之讥。吾敢以是艾君之癖。君其有意乎。姑书诗轴上以俟。君名之翰字乃宪。与余最相善。宅边有文杏树亭亭可爱。是为君日哦之所。仍以自号云。金后庵遗集序
吾东都古称多硕德文章之士。而安康县在东都。尤有称焉。盖以大贤桑梓之里。在县之东。俎豆之院。在县之西。其遗风剩馥之及于后者然也。试以百年前言之。有若鲁庵金公,竹轩李公,蒙庵李公在县东西。而后庵金公居其中。于鲁庵则尊事之。于竹轩蒙庵则切磋之。俱以硕德文章。有名于时。而至今为东都后生之称诵焉。树仁生也晚。未及抠衣于几席之下。而只有旷世缅仰之怀。间者后庵公五世孙最重袖遗集一册来示之。始得盥手奉阅焉。则文章赡富。不雕不饰。惟意之适。真所谓德性之蕴而发于外者。第
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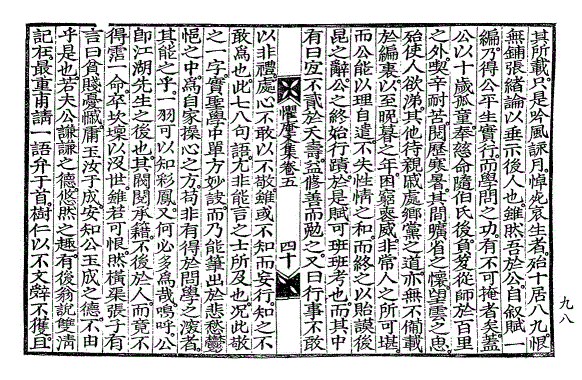 其所载。只是吟风咏月。悼死哀生者。殆十居八九。恨无铺张绪论以垂示后人也。虽然吾于公。自叙赋一编。乃得公平生实行。而学问之功。有不可掩者矣。盖公以十岁孤童。奉慈命随伯氏后。负笈从师于百里之外。吃辛耐苦。阅历寒暑。其间旷省之怀。望云之思。殆使人欲涕。其他待亲戚处乡党之道。亦无不备载于编里。以至晚暮之年。困穷丧威。非常人之所可堪。而公能以理自遣。不失性情之和。而终之以贻谟后昆之辞。公之终始行迹。于是赋可班班考也。而其中有曰宜不贰于夭寿。益修善而勉之。又曰行事不敢以非礼。处心不敢以不敬。虽或不知而妄行。知之不敢为也。此七八句语。尤非能言之士所及也。况此敬之一字。实圣学中单方妙诀。而乃能笔出于悲愁郁悒之中。为自家操心之方。苟非有得于问学之深者。其能之乎。一羽可以知彩凤。又何必多为哉。呜呼。公即江湖先生之后也。其阀阅承籍。不后于人。而竟不得沾一命。卒坎壈以没世。虽若可恨。然横渠张子有言曰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安知公玉成之德。不由乎是也。若夫公谦谦之德。悠然之趣。有后翁说双清记在。最重甫请一语弁于首。树仁以不文辞不获。且
其所载。只是吟风咏月。悼死哀生者。殆十居八九。恨无铺张绪论以垂示后人也。虽然吾于公。自叙赋一编。乃得公平生实行。而学问之功。有不可掩者矣。盖公以十岁孤童。奉慈命随伯氏后。负笈从师于百里之外。吃辛耐苦。阅历寒暑。其间旷省之怀。望云之思。殆使人欲涕。其他待亲戚处乡党之道。亦无不备载于编里。以至晚暮之年。困穷丧威。非常人之所可堪。而公能以理自遣。不失性情之和。而终之以贻谟后昆之辞。公之终始行迹。于是赋可班班考也。而其中有曰宜不贰于夭寿。益修善而勉之。又曰行事不敢以非礼。处心不敢以不敬。虽或不知而妄行。知之不敢为也。此七八句语。尤非能言之士所及也。况此敬之一字。实圣学中单方妙诀。而乃能笔出于悲愁郁悒之中。为自家操心之方。苟非有得于问学之深者。其能之乎。一羽可以知彩凤。又何必多为哉。呜呼。公即江湖先生之后也。其阀阅承籍。不后于人。而竟不得沾一命。卒坎壈以没世。虽若可恨。然横渠张子有言曰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安知公玉成之德。不由乎是也。若夫公谦谦之德。悠然之趣。有后翁说双清记在。最重甫请一语弁于首。树仁以不文辞不获。且惧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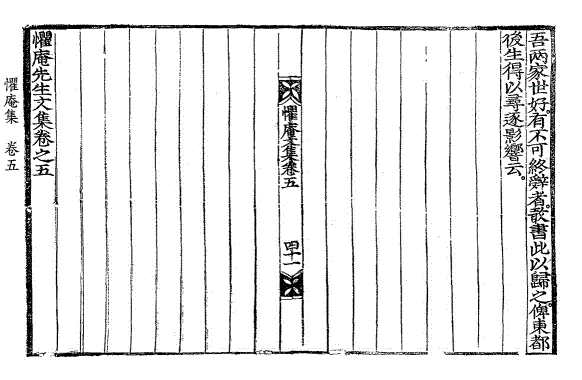 吾两家世好。有不可终辞者。敢书此以归之。俾东都后生得以寻逐影响云。
吾两家世好。有不可终辞者。敢书此以归之。俾东都后生得以寻逐影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