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书
书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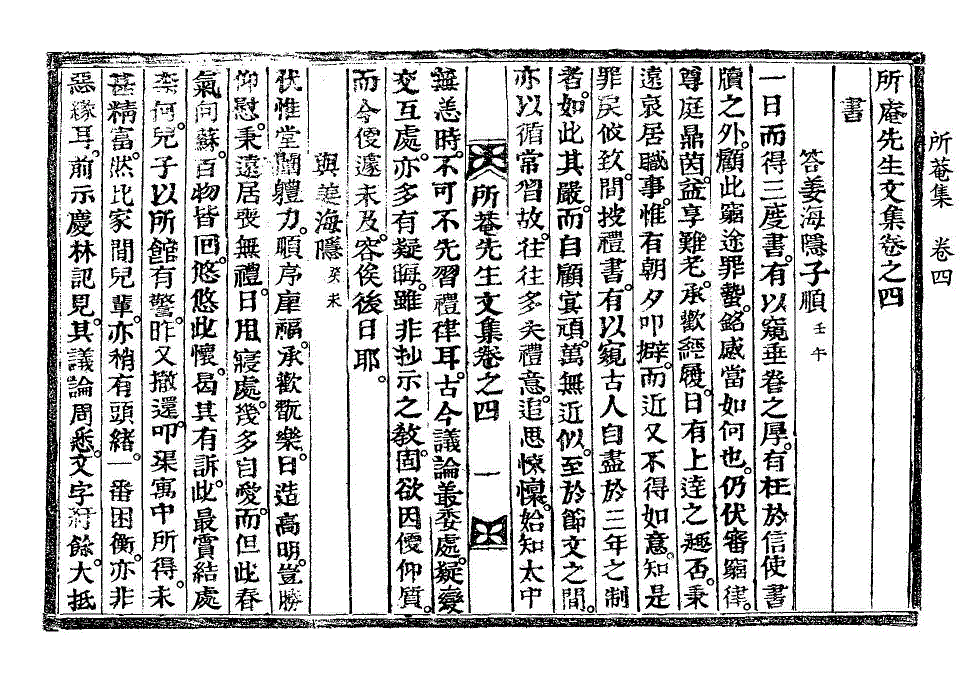 答姜海隐子顺(壬午)
答姜海隐子顺(壬午)一日而得三度书。有以窥垂眷之厚。有在于信使书牍之外。顾此穷途罪蛰。铭感当如何也。仍伏审穷律。尊庭鼎茵。益享难老。承欢经履。日有上达之趣否。秉远哀居职事。惟有朝夕叩擗。而近又不得如意。知是罪戾攸致。间披礼书。有以窥古人自尽于三年之制者。如此其严。而自顾冥顽。万无近似。至于节文之间。亦以循常习故。往往多失礼意。追思悚懔。始知太中无恙时。不可不先习礼律耳。古今议论丛委处。疑变交互处。亦多有疑晦。虽非抄示之教。固欲因便仰质。而今便遽未及。容俟后日耶。
与姜海隐(癸未)
伏惟堂闱体力。顺序康福。承欢玩乐。日造高明。岂胜仰慰。秉远居丧无礼。日用寝处。几多自爱。而但此春气向苏。百物皆回。悠悠此怀。曷其有诉。此最霣结处柰何。儿子以所馆有警。昨又撤还。叩渠寓中所得。未甚精富。然比家间儿辈。亦稍有头绪。一番困衡。亦非恶缘耳。前示庆林记见。其议论周悉。文字纡馀。大抵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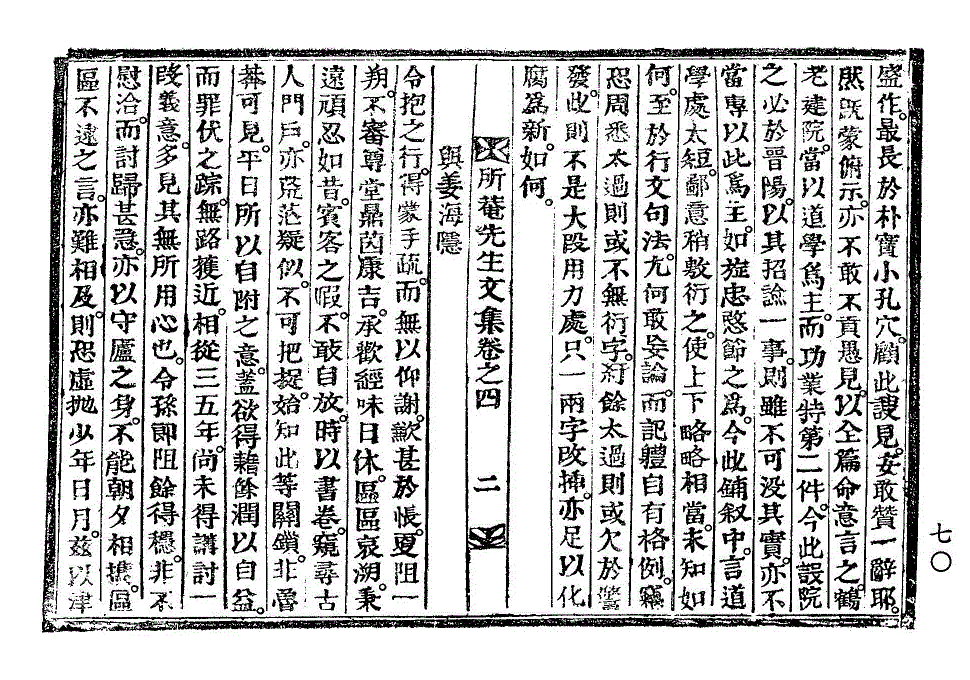 盛作。最长于朴实小孔穴。顾此謏见。安敢赞一辞耶。然既蒙俯示。亦不敢不贡愚见。以全篇命意言之。鹤老建院。当以道学为主。而功业特第二件。今此设院之必于晋阳。以其招谕一事。则虽不可没其实。亦不当专以此为主。如旌忠悯节之为。今此铺叙中。言道学处太短。鄙意稍敷衍之。使上下略略相当。未知如何。至于行文句法。尤何敢妄论。而记体自有格例。窃恐周悉太过则或不无衍字。纡馀太过则或欠于警发。此则不是大段用力处。只一两字改插。亦足以化腐为新。如何。
盛作。最长于朴实小孔穴。顾此謏见。安敢赞一辞耶。然既蒙俯示。亦不敢不贡愚见。以全篇命意言之。鹤老建院。当以道学为主。而功业特第二件。今此设院之必于晋阳。以其招谕一事。则虽不可没其实。亦不当专以此为主。如旌忠悯节之为。今此铺叙中。言道学处太短。鄙意稍敷衍之。使上下略略相当。未知如何。至于行文句法。尤何敢妄论。而记体自有格例。窃恐周悉太过则或不无衍字。纡馀太过则或欠于警发。此则不是大段用力处。只一两字改插。亦足以化腐为新。如何。与姜海隐
令抱之行。得蒙手疏。而无以仰谢。歉甚于怅。更阻一朔。不审尊堂鼎茵康吉。承欢经味日休。区区哀溯。秉远顽忍如昔。宾客之暇。不敢自放。时以书卷。窥寻古人门户。亦荒茫疑似。不可把捉。始知此等关锁。非鲁莽可见。平日所以自附之意。盖欲得藉馀润以自益。而罪伏之踪。无路获近。相从三五年。尚未得讲讨一段义意。多见其无所用心也。令孙郎阻馀得稳。非不慰洽。而讨归甚急。亦以守庐之身。不能朝夕相携。区区不逮之言。亦难相及。则恐虚抛少年日月。玆以津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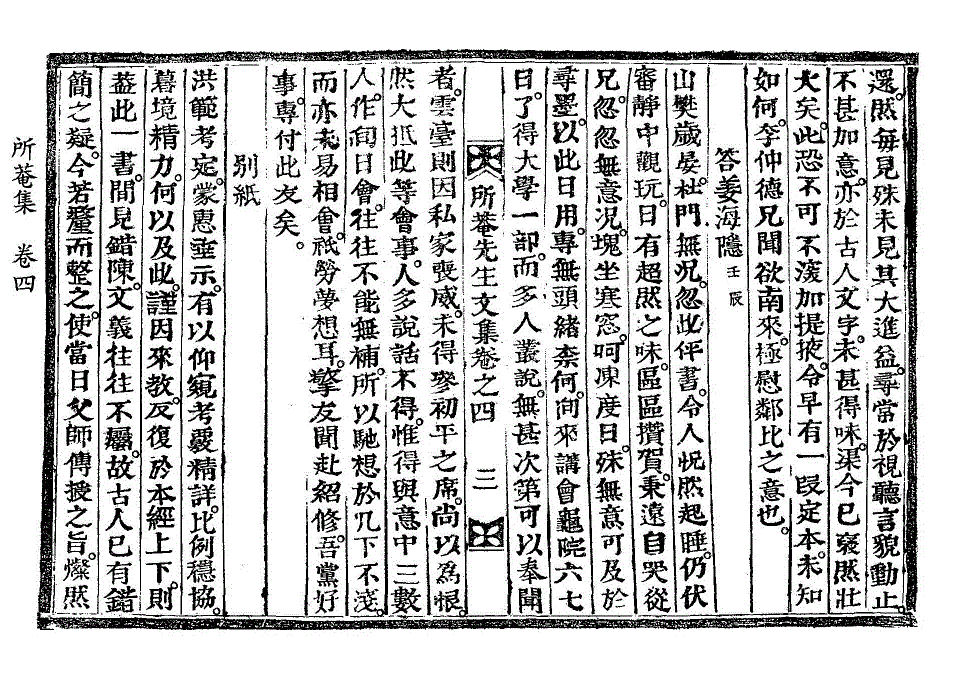 还。然每见殊未见其大进益。寻常于视听言貌动止。不甚加意。亦于古人文字。未甚得味。渠今已褒然壮大矣。此恐不可不深加提掖。令早有一段定本。未知如何。李仲德兄闻欲南来。极慰邻比之意也。
还。然每见殊未见其大进益。寻常于视听言貌动止。不甚加意。亦于古人文字。未甚得味。渠今已褒然壮大矣。此恐不可不深加提掖。令早有一段定本。未知如何。李仲德兄闻欲南来。极慰邻比之意也。答姜海隐(壬辰)
山樊岁晏。杜门无况。忽此伻书。令人恍然起睡。仍伏审静中观玩。日有超然之味。区区攒贺。秉远自哭从兄。忽忽无意况。块坐寒窗。呵冻度日。殊无意可及于寻墨。以此日用。专无头绪柰何。向来讲会龟院六七日。了得大学一部。而多人丛说。无甚次第可以奉闻者。云台则因私家丧威。未得参初平之席。尚以为恨。然大抵此等会事。人多说话不得。惟得与意中三数人。作旬日会。往往不能无补。所以驰想于几下不浅。而亦未易相会。祇劳梦想耳。擎友闻赴绍修。吾党好事。专付此友矣。
别纸
洪范考定。蒙惠垂示。有以仰窥考覈精详。比例稳协。暮境精力。何以及此。谨因来教。反复于本经上下。则盖此一书。间见错陈。文义往往不属。故古人已有错简之疑。今若釐而整之。使当日父师传授之旨。灿然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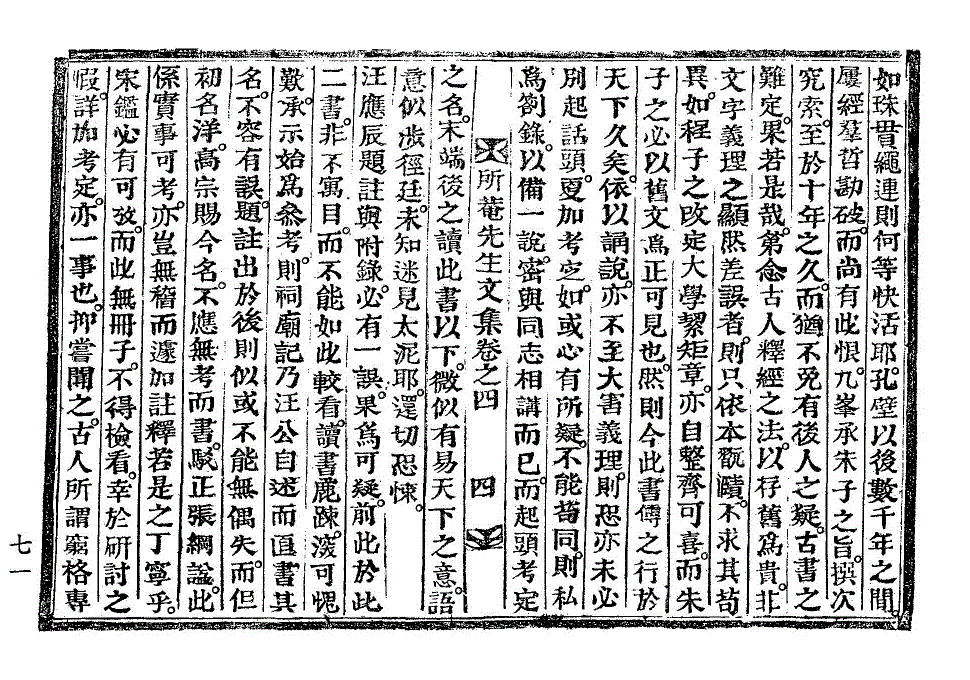 如珠贯绳连则何等快活耶。孔壁以后数千年之间。屡经群哲勘破。而尚有此恨。九峰承朱子之旨。撰次究索。至于十年之久。而犹不免有后人之疑。古书之难定。果若是哉。第念古人释经之法。以存旧为贵。非文字义理之显然差误者。则只依本玩赜。不求其苟异。如程子之改定大学絜矩章。亦自整齐可喜。而朱子之必以旧文为正可见也。然则今此书传之行于天下久矣。依以诵说。亦不至大害义理。则恐亦未必别起话头。更加考定。如或心有所疑。不能苟同。则私为劄录。以备一说。密与同志相讲而已。而起头考定之名。末端后之读此书以下。微似有易天下之意。语意似涉径廷。未知迷见太泥耶。还切恐悚。
如珠贯绳连则何等快活耶。孔壁以后数千年之间。屡经群哲勘破。而尚有此恨。九峰承朱子之旨。撰次究索。至于十年之久。而犹不免有后人之疑。古书之难定。果若是哉。第念古人释经之法。以存旧为贵。非文字义理之显然差误者。则只依本玩赜。不求其苟异。如程子之改定大学絜矩章。亦自整齐可喜。而朱子之必以旧文为正可见也。然则今此书传之行于天下久矣。依以诵说。亦不至大害义理。则恐亦未必别起话头。更加考定。如或心有所疑。不能苟同。则私为劄录。以备一说。密与同志相讲而已。而起头考定之名。末端后之读此书以下。微似有易天下之意。语意似涉径廷。未知迷见太泥耶。还切恐悚。汪应辰题注与附录。必有一误。果为可疑。前此于此二书。非不寓目。而不能如此较看。读书粗疏。深可愧叹。承示始为参考。则祠庙记乃汪公自述而直书其名。不容有误。题注出于后则似或不能无偶失。而但初名洋。高宗赐今名。不应无考而书。驳正张纲谥。此系实事可考。亦岂无稽而遽加注释若是之丁宁乎。宋鉴必有可考。而此无册子。不得检看。幸于研讨之暇。详加考定。亦一事也。抑尝闻之。古人所谓穷格专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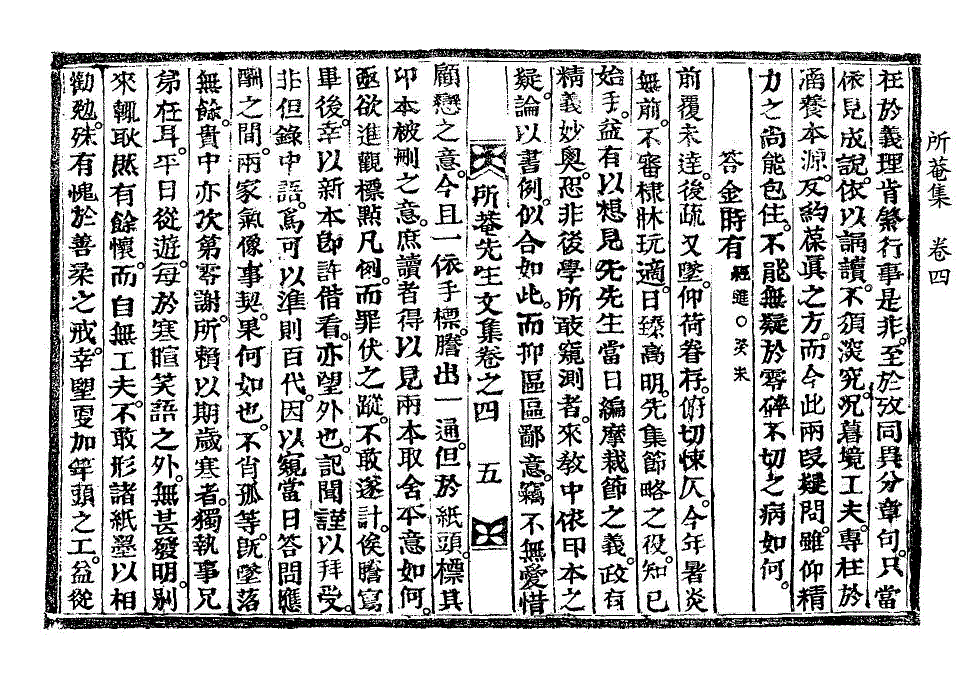 在于义理肯綮行事是非。至于考同异分章句。只当依见成说。依以诵读。不须深究。况暮境工夫。专在于涵养本源。反约葆真之方。而今此两段疑问。虽仰精力之尚能包住。不能无疑于零碎不切之病如何。
在于义理肯綮行事是非。至于考同异分章句。只当依见成说。依以诵读。不须深究。况暮境工夫。专在于涵养本源。反约葆真之方。而今此两段疑问。虽仰精力之尚能包住。不能无疑于零碎不切之病如何。答金时有(经进○癸未)
前覆未达。后疏又坠。仰荷眷存。俯切悚仄。今年暑炎无前。不审棣床玩适。日臻高明。先集节略之役。知已始手。益有以想见先先生当日编摩裁节之义。政有精义妙奥。恐非后学所敢窥测者。来教中依印本之疑。论以书例。似合如此。而抑区区鄙意。窃不无爱惜顾恋之意。今且一依手标。誊出一通。但于纸头。标其印本被删之意。庶读者得以见两本取舍本意如何。亟欲进观标点凡例。而罪伏之踪。不敢遂计。俟誊写毕后。幸以新本即许借看。亦望外也。记闻谨以拜受。非但录中语。为可以准则百代。因以窥当日答问应酬之间。两家气像事契。果何如也。不肖孤等。既坠落无馀。贵中亦次第零谢。所赖以期岁寒者。独执事兄弟在耳。平日从游。每于寒暄笑语之外。无甚发明。别来辄耿然有馀怀。而自无工夫。不敢形诸纸墨以相劝勉。殊有愧于善柔之戒。幸望更加竿头之工。益从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2L 页
 事于遗书中。时以所得馀润。相反复提谕。俾此愚滞。亦得有所持循焉如何。
事于遗书中。时以所得馀润。相反复提谕。俾此愚滞。亦得有所持循焉如何。答金德明(诚进○甲午)
如丧之痛。普率惟均。隔岑之地。不相往还。今几时矣。瞻耿何尝小弛。而懒于笔研。不能谋一候。乃蒙长笺。寄意郑重。自顾贱弊。何以获此。拜读感愧。仍审穷律。静履玩养崇深。仰慰不胜。秉远未老而衰。不病而瘁。兄弟相对。相怜而已。朋友相爱者。不知此间实状。或意关门块伏之中。有事于故纸堆中。往往以不称之语相问。每一承读。辄增惶汗。吾辈老而无闻。使家先辛勤收拾之物。一向放顿坠失。诚觉得罪父师。今虽耄及。犹可策励自新。免为法门弃物。幸以玩养之馀。时赐鞕策。亦君子及物之仁也。柳令遇巷之初。遽遭遗剑之痛。亦恐是运气致然。闻其已寻遂初。而但闻病情颇有根株。为之忧念耳。岁险振古未有。剥床之忧。无处不然。未知几时可得清平界。相会如曩时耶。只切瞻想。
答柳敬缉(德祚○癸酉)
俯枉之厚未谢。而辱问之勤遽及。感愧并之。仍审日来。玩乐超谧。秉远看当巨役。殊觉费心力。但赖有三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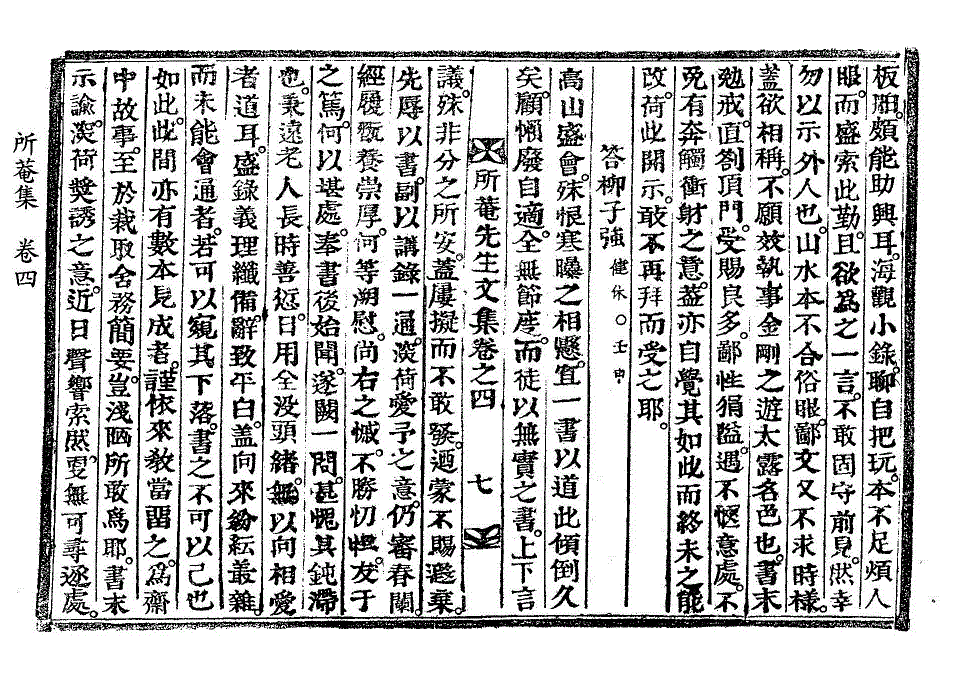 板舶。颇能助兴耳。海观小录。聊自把玩。本不足烦人眼。而盛索此勤。且欲为之一言。不敢固守前见。然幸勿以示外人也。山水本不合俗眼。鄙文又不求时样。盖欲相称。不愿效执事金刚之游太露名色也。书末勉戒。直劄顶门。受赐良多。鄙性狷隘。遇不惬意处。不免有奔触冲射之意。盖亦自觉其如此而终未之能改。荷此开示。敢不再拜而受之耶。
板舶。颇能助兴耳。海观小录。聊自把玩。本不足烦人眼。而盛索此勤。且欲为之一言。不敢固守前见。然幸勿以示外人也。山水本不合俗眼。鄙文又不求时样。盖欲相称。不愿效执事金刚之游太露名色也。书末勉戒。直劄顶门。受赐良多。鄙性狷隘。遇不惬意处。不免有奔触冲射之意。盖亦自觉其如此而终未之能改。荷此开示。敢不再拜而受之耶。答柳子强(健休○壬申)
高山盛会。殊恨寒曝之相悬。宜一书以道此倾倒久矣。顾懒废自适。全无节度。而徒以无实之书。上下言议。殊非分之所安。盖屡拟而不敢发。乃蒙不赐遐弃。先辱以书。副以讲录一通。深荷爱予之意。仍审春阑。经履玩养崇厚。何等溯慰。尚右之戚。不胜忉怛。友于之笃。何以堪处。奉书后始闻。遂阙一问。甚愧其钝滞也。秉远老人长时善愆。日用全没头绪。无以向相爱者道耳。盛录义理纤备。辞致平白。盖向来纷纭丛杂。而未能会通者。若可以窥其下落。书之不可以已也如此。此间亦有数本见成者。谨依来教当留之。为斋中故事。至于裁取舍务简要。岂浅陋所敢为耶。书末示谕。深荷奖诱之意。近日声响索然。更无可寻逐处。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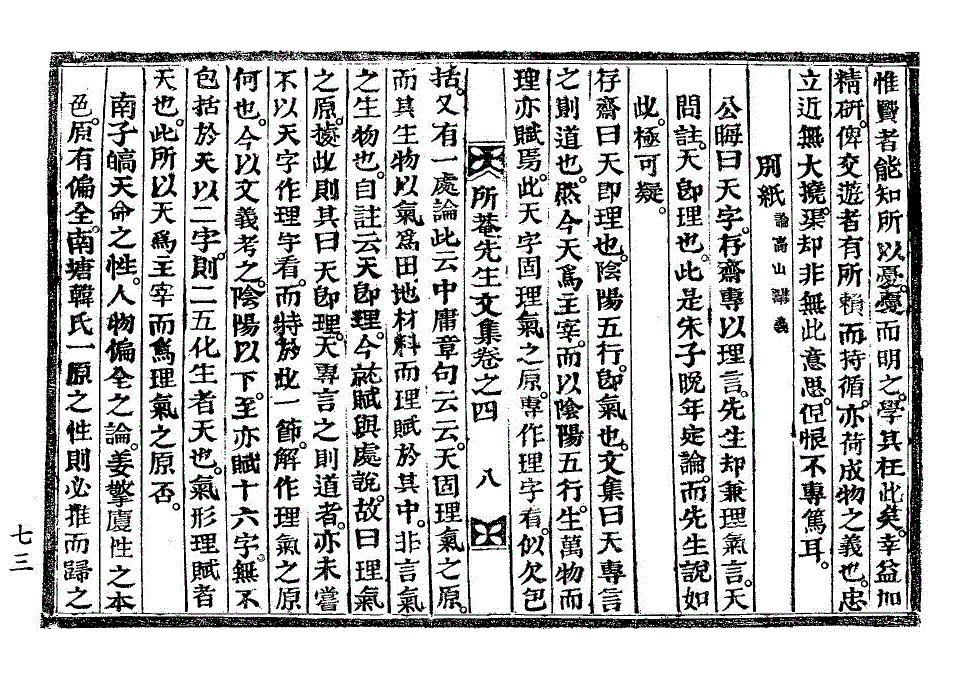 惟贤者能知所以忧。忧而明之。学其在此矣。幸益加精研。俾交游者有所赖而持循。亦荷成物之义也。忠立近无大挠。渠却非无此意思。但恨不专笃耳。
惟贤者能知所以忧。忧而明之。学其在此矣。幸益加精研。俾交游者有所赖而持循。亦荷成物之义也。忠立近无大挠。渠却非无此意思。但恨不专笃耳。别纸(论高山讲义)
公晦曰天字。存斋专以理言。先生却兼理气言。天问注。天即理也。此是朱子晚年定论。而先生说如此。极可疑。
存斋曰天即理也。阴阳五行。即气也。文集曰天专言之则道也。然今天为主宰。而以阴阳五行。生万物而理亦赋焉。此天字固理气之原。专作理字看。似欠包括。又有一处论此云中庸章句云云。天固理气之原。而其生物以气为田地材料而理赋于其中。非言气之生物也。自注云天即理。今就赋与处说。故曰理气之原。据此则其曰天即理。天专言之则道者。亦未尝不以天字作理字看。而特于此一节。解作理气之原何也。今以文义考之。阴阳以下。至亦赋十六字。无不包括于天以二字。则二五化生者天也。气形理赋者天也。此所以天为主宰而为理气之原否。
南子皓天命之性。人物偏全之论。姜擎厦性之本色。原有偏全。南塘韩氏一原之性则必推而归之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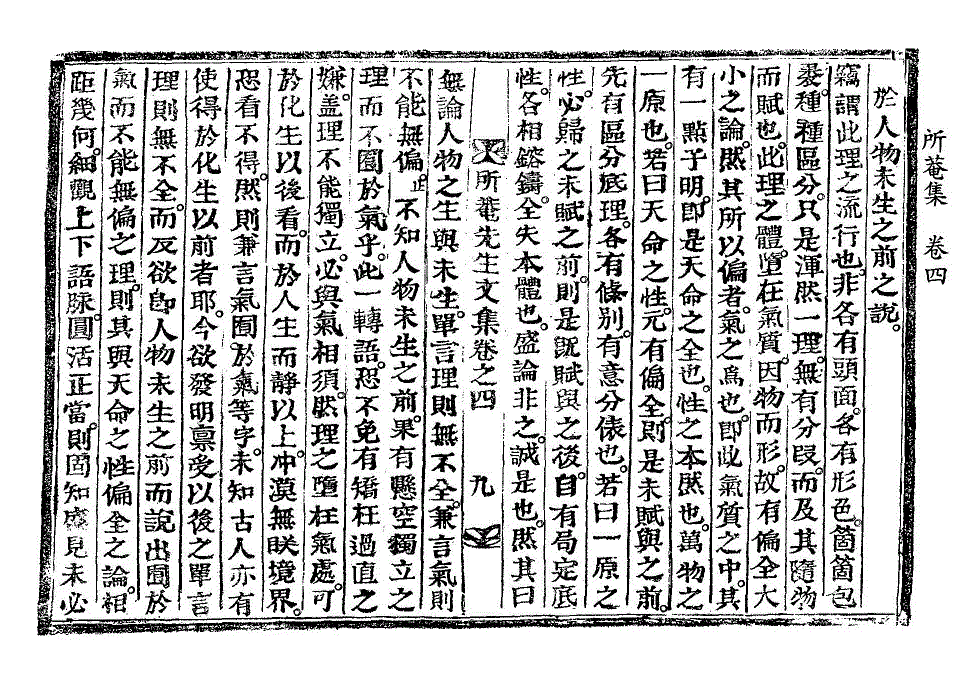 于人物未生之前之说。
于人物未生之前之说。窃谓此理之流行也。非各有头面。各有形色。个个包裹。种种区分。只是浑然一理。无有分段。而及其随物而赋也。此理之体。堕在气质。因物而形。故有偏全大小之论。然其所以偏者。气之为也。即此气质之中。其有一点子明。即是天命之全也。性之本然也。万物之一原也。若曰天命之性。元有偏全。则是未赋与之前。先有区分底理。各有条别。有意分俵也。若曰一原之性。必归之未赋之前。则是既赋与之后。自有局定底性。各相镕铸。全失本体也。盛论非之。诚是也。然其曰无论人物之生与未生。单言理则无不全。兼言气则不能无偏。(止)不知人物未生之前。果有悬空独立之理而不囿于气乎。此一转语。恐不免有矫枉过直之嫌。盖理不能独立。必与气相须。然理之堕在气处。可于化生以后看。而于人生而静以上。冲漠无眹境界。恐看不得。然则兼言气囿于气等字。未知古人亦有使得于化生以前者耶。今欲发明禀受以后之单言理则无不全。而反欲即人物未生之前而说出囿于气而不能无偏之理。则其与天命之性偏全之论。相距几何。细观上下语脉。圆活正当。则固知盛见未必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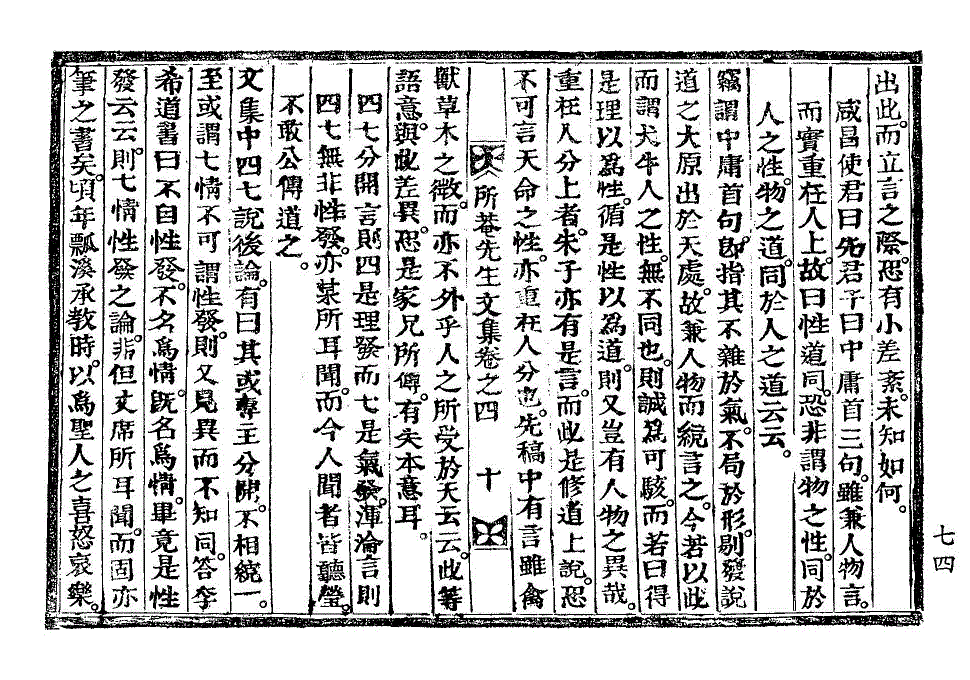 出此。而立言之际。恐有小差紊。未知如何。
出此。而立言之际。恐有小差紊。未知如何。咸昌使君曰先君子曰中庸首三句。虽兼人物言。而实重在人上。故曰性道同。恐非谓物之性。同于人之性。物之道。同于人之道云云。
窃谓中庸首句。即指其不杂于气。不局于形。剔发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处。故兼人物而统言之。今若以此而谓犬牛人之性。无不同也。则诚为可骇。而若曰得是理以为性。循是性以为道。则又岂有人物之异哉。重在人分上者。朱子亦有是言。而此是修道上说。恐不可言天命之性。亦重在人分也。先稿中有言虽禽兽草木之微。而亦不外乎人之所受于天云云。此等语意。与此差异。恐是家兄所传。有失本意耳。
四七分开言则四是理发而七是气发。浑沦言则四七无非性发。亦某所耳闻。而今人闻者皆听莹。不敢公传道之。
文集中四七说后论。有曰其或专主分开。不相统一。至或谓七情不可谓性发。则又见异而不知同。答李希道书曰不自性发。不名为情。既名为情。毕竟是性发云云。则七情性发之论。非但丈席所耳闻。而固亦笔之书矣。顷年瓢溪承教时。以为圣人之喜怒哀乐。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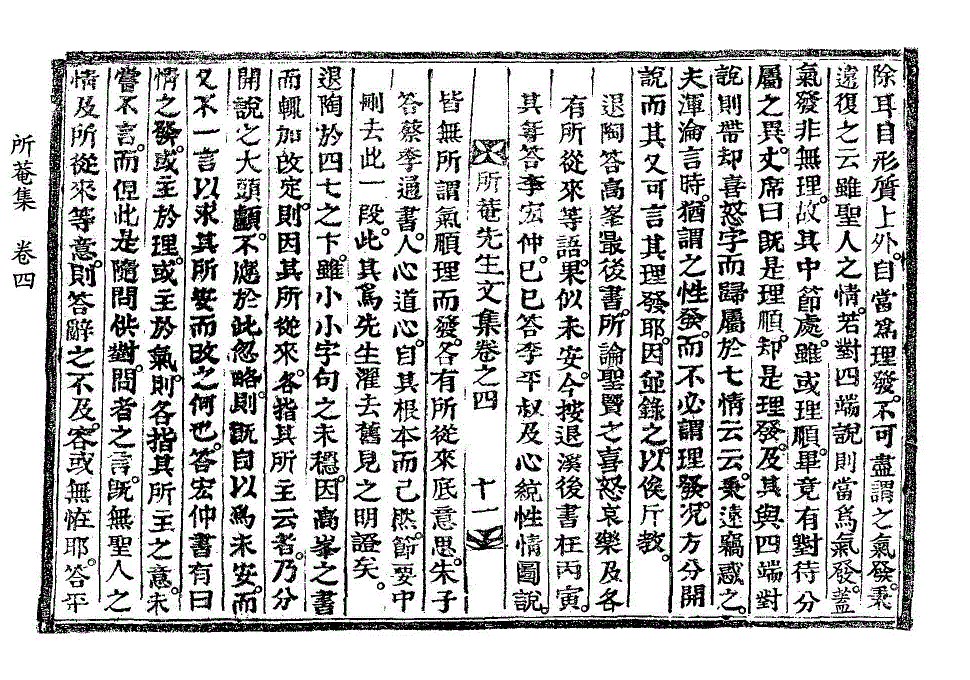 除耳目形质上外。自当为理发。不可尽谓之气发。秉远复之云虽圣人之情。若对四端说则当为气发。盖气发非无理。故其中节处。虽或理顺。毕竟有对待分属之异。丈席曰既是理顺。却是理发。及其与四端对说则带却喜怒字而归属于七情云云。秉远窃惑之。夫浑沦言时。犹谓之性发。而不必谓理发。况方分开说而其又可言其理发耶。因并录之。以俟斤教。
除耳目形质上外。自当为理发。不可尽谓之气发。秉远复之云虽圣人之情。若对四端说则当为气发。盖气发非无理。故其中节处。虽或理顺。毕竟有对待分属之异。丈席曰既是理顺。却是理发。及其与四端对说则带却喜怒字而归属于七情云云。秉远窃惑之。夫浑沦言时。犹谓之性发。而不必谓理发。况方分开说而其又可言其理发耶。因并录之。以俟斤教。退陶答高峰最后书。所论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语。果似未安。今按退溪后书在丙寅。其年答李宏仲。己巳答李平叔及心统性情图说。皆无所谓气顺理而发。各有所从来底意思。朱子答蔡季通书。人心道心。自其根本而已然。节要中删去此一段。此其为先生濯去旧见之明證矣。
退陶于四七之卞。虽小小字句之未稳。因高峰之书而辄加改定。则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云者。乃分开说之大头颅。不应于此忽略。则既自以为未安。而又不一言以求其所安而改之何也。答宏仲书有曰情之发。或主于理。或主于气。则各指其所主之意。未尝不言。而但此是随问供对。问者之言。既无圣人之情及所从来等意。则答辞之不及。容或无怪耶。答平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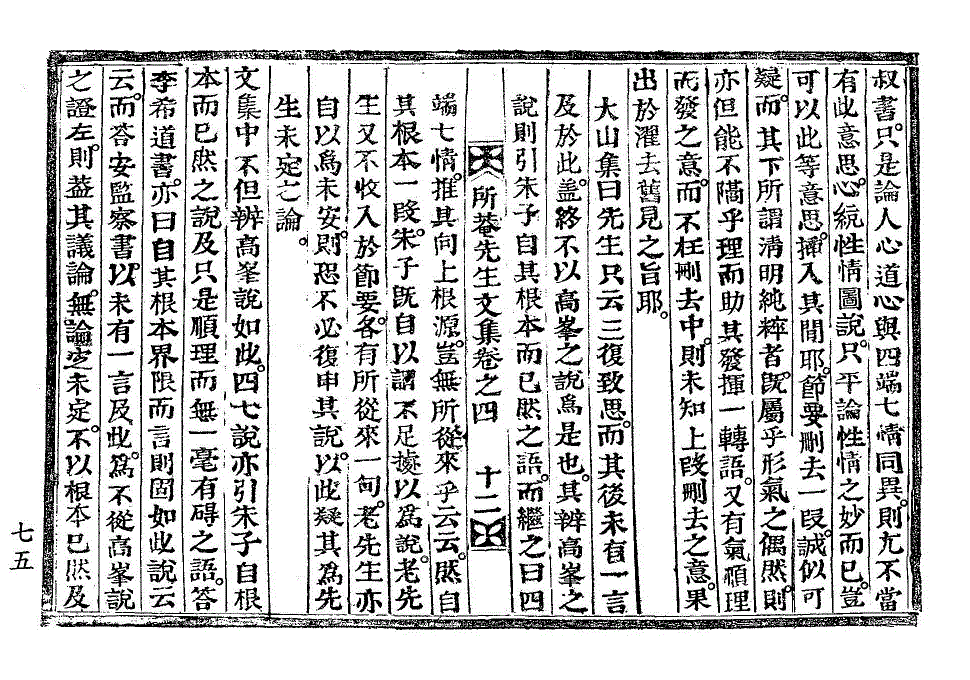 叔书。只是论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同异。则尤不当有此意思。心统性情图说。只平论性情之妙而已。岂可以此等意思。插入其间耶。节要删去一段。诚似可疑。而其下所谓清明纯粹者。既属乎形气之偶然。则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一转语。又有气顺理而发之意。而不在删去中。则未知上段删去之意。果出于濯去旧见之旨耶。
叔书。只是论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同异。则尤不当有此意思。心统性情图说。只平论性情之妙而已。岂可以此等意思。插入其间耶。节要删去一段。诚似可疑。而其下所谓清明纯粹者。既属乎形气之偶然。则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一转语。又有气顺理而发之意。而不在删去中。则未知上段删去之意。果出于濯去旧见之旨耶。大山集曰先生只云三复致思。而其后未有一言及于此。盖终不以高峰之说为是也。其辨高峰之说则引朱子自其根本而已然之语。而继之曰四端七情。推其向上根源。岂无所从来乎云云。然自其根本一段。朱子既自以谓不足据以为说。老先生又不收入于节要。各有所从来一句。老先生亦自以为未安。则恐不必复申其说。以此疑其为先生未定之论。
文集中不但辨高峰说如此。四七说亦引朱子自根本而已然之说及只是顺理而无一毫有碍之语。答李希道书。亦曰自其根本界限而言则固如此说云云。而答安监察书。以未有一言及此。为不从高峰说之證左。则盖其议论。无论定未定。不以根本已然及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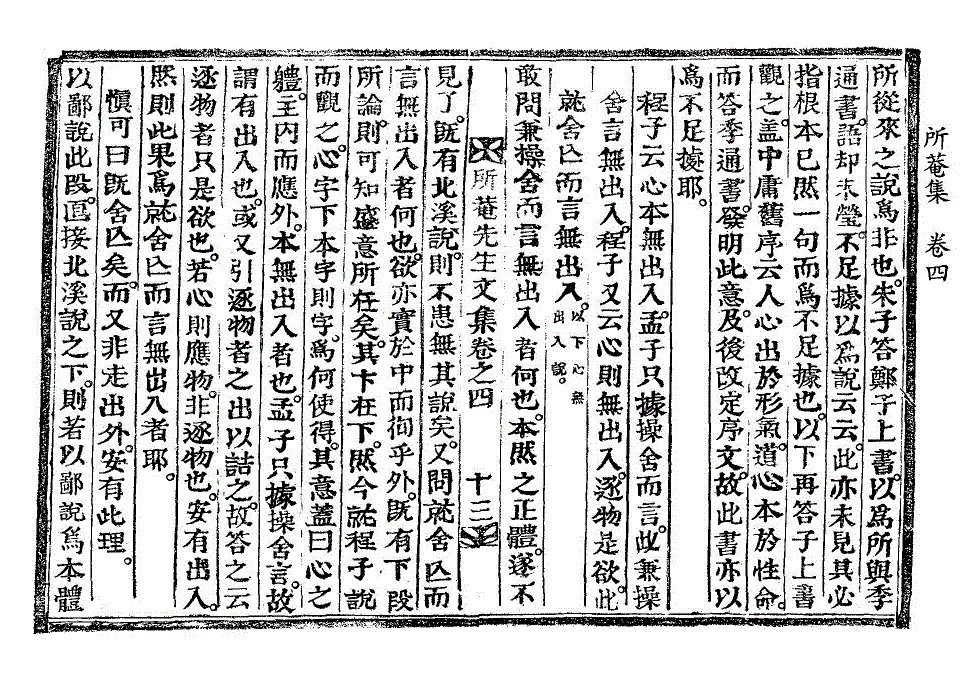 所从来之说为非也。朱子答郑子上书。以为所与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云云。此亦未见其必指根本已然一句而为不足据也。以下再答子上书观之。盖中庸旧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发明此意。及后改定序文。故此书亦以为不足据耶。
所从来之说为非也。朱子答郑子上书。以为所与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云云。此亦未见其必指根本已然一句而为不足据也。以下再答子上书观之。盖中庸旧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发明此意。及后改定序文。故此书亦以为不足据耶。程子云心本无出入。孟子只据操舍而言。此兼操舍言无出入。程子又云心则无出入。逐物是欲。此就舍亡而言无出入。(以下心无出入说。)
敢问兼操舍而言无出入者何也。本然之正体。遂不见了。既有北溪说。则不患无其说矣。又问就舍亡而言无出入者何也。欲亦实于中而徇乎外。既有下段所论。则可知盛意所在矣。其卞在下。然今就程子说而观之。心字下本字则字。为何使得。其意盖曰心之体。主内而应外。本无出入者也。孟子只据操舍言。故谓有出入也。或又引逐物者之出以诘之。故答之云逐物者只是欲也。若心则应物。非逐物也。安有出入。然则此果为就舍亡而言无出入者耶。
慎可曰既舍亡矣。而又非走出外。安有此理。
以鄙说此段。直接北溪说之下。则若以鄙说为本体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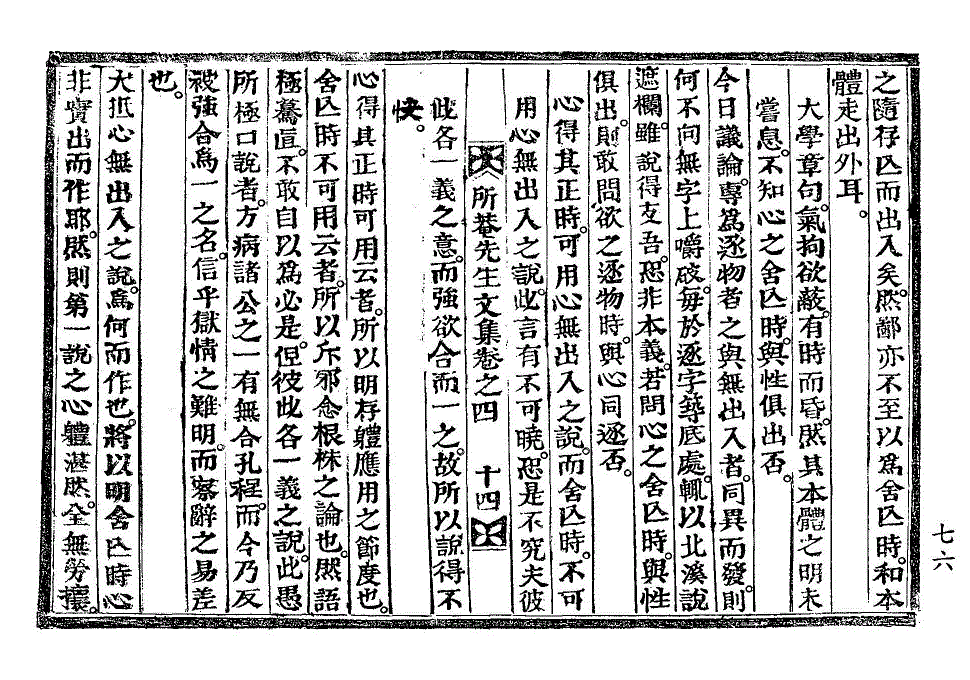 之随存亡而出入矣。然鄙亦不至以为舍亡时。和本体走出外耳。
之随存亡而出入矣。然鄙亦不至以为舍亡时。和本体走出外耳。大学章句。气拘欲蔽。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未尝息。不知心之舍亡时。与性俱出否。
今日议论。专为逐物者之与无出入者。同异而发。则何不向无字上嚼破。每于逐字筑底处。辄以北溪说遮栏。虽说得支吾。恐非本义。若问心之舍亡时。与性俱出。则敢问欲之逐物时。与心同逐否。
心得其正时。可用心无出入之说。而舍亡时。不可用心无出入之说。此言有不可晓。恐是不究夫彼此各一义之意。而强欲合而一之。故所以说得不快。
心得其正时可用云者。所以明存体应用之节度也。舍亡时不可用云者。所以斥邪念根株之论也。然语极蓦直。不敢自以为必是。但彼此各一义之说。此愚所极口说者。方病诸公之一有无合孔程。而今乃反被强合为一之名。信乎狱情之难明。而察辞之易差也。
大抵心无出入之说。为何而作也。将以明舍亡时心非实出而作耶。然则第一说之心体湛然。全无劳攘。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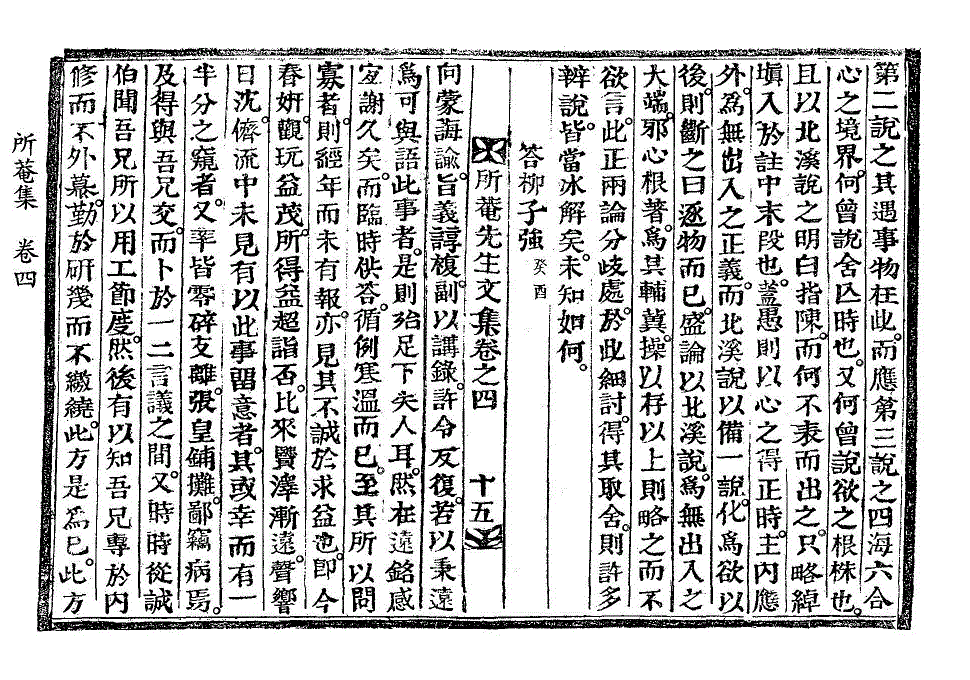 第二说之其遇事物在此。而应第三说之四海六合心之境界。何曾说舍亡时也。又何曾说欲之根株也。且以北溪说之明白指陈。而何不表而出之。只略绰填入于注中末段也。盖愚则以心之得正时。主内应外。为无出入之正义。而北溪说以备一说。化为欲以后。则断之曰逐物而已。盛论以北溪说。为无出入之大端。邪心根著。为其辅冀。操以存以上则略之而不欲言。此正两论分歧处。于此细讨。得其取舍。则许多辨说。皆当冰解矣。未知如何。
第二说之其遇事物在此。而应第三说之四海六合心之境界。何曾说舍亡时也。又何曾说欲之根株也。且以北溪说之明白指陈。而何不表而出之。只略绰填入于注中末段也。盖愚则以心之得正时。主内应外。为无出入之正义。而北溪说以备一说。化为欲以后。则断之曰逐物而已。盛论以北溪说。为无出入之大端。邪心根著。为其辅冀。操以存以上则略之而不欲言。此正两论分歧处。于此细讨。得其取舍。则许多辨说。皆当冰解矣。未知如何。答柳子强(癸酉)
向蒙诲谕。旨义谆复。副以讲录。许令反复。若以秉远为可与语此事者。是则殆足下失人耳。然在远铭感宜谢久矣。而临时供答。循例寒温而已。至其所以问寡者。则经年而未有报。亦见其不诚于求益也。即今春妍。观玩益茂。所得益超诣否。比来贤泽渐远。声响日沈。侪流中未见有以此事留意者。其或幸而有一半分之窥者。又率皆零碎支离。张皇铺摊。鄙窃病焉。及得与吾兄交。而卜于一二言议之间。又时时从诚伯闻吾兄所以用工节度。然后有以知吾兄专于内修而不外慕。勤于研几而不缴绕。此方是为己。此方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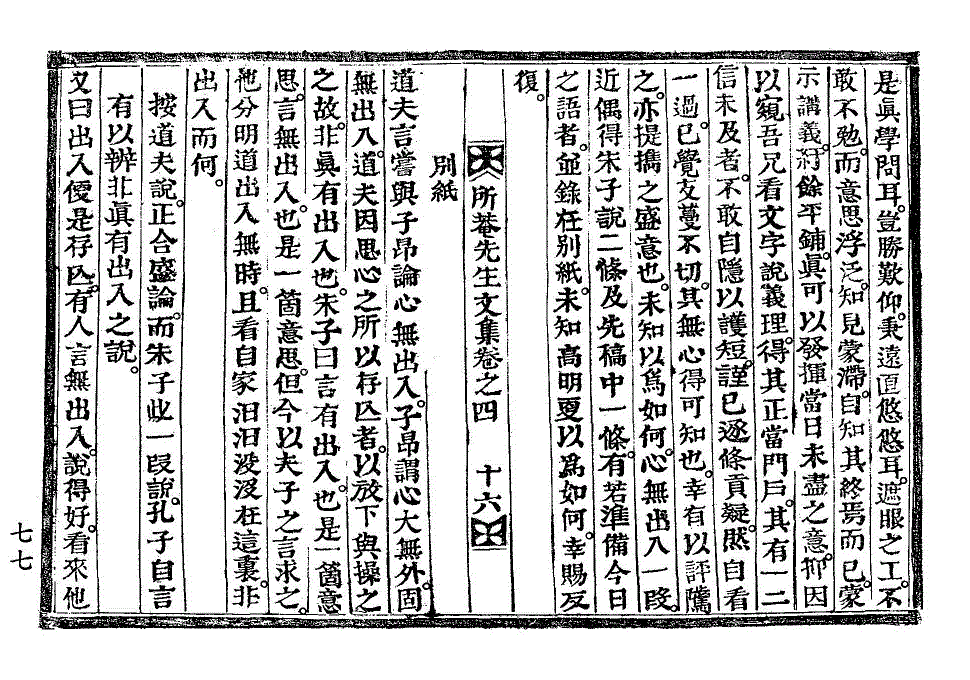 是真学问耳。岂胜叹仰。秉远直悠悠耳。遮眼之工。不敢不勉。而意思浮泛。知见蒙滞。自知其终焉而已。蒙示讲义。纡馀平铺。真可以发挥当日未尽之意。抑因以窥吾兄看文字说义理。得其正当门户。其有一二信未及者。不敢自隐以护短。谨已逐条贡疑。然自看一过。已觉支蔓不切。其无心得可知也。幸有以评骘之。亦提携之盛意也。未知以为如何。心无出入一段。近偶得朱子说二条及先稿中一条。有若准备今日之语者。并录在别纸。未知高明更以为如何。幸赐反复。
是真学问耳。岂胜叹仰。秉远直悠悠耳。遮眼之工。不敢不勉。而意思浮泛。知见蒙滞。自知其终焉而已。蒙示讲义。纡馀平铺。真可以发挥当日未尽之意。抑因以窥吾兄看文字说义理。得其正当门户。其有一二信未及者。不敢自隐以护短。谨已逐条贡疑。然自看一过。已觉支蔓不切。其无心得可知也。幸有以评骘之。亦提携之盛意也。未知以为如何。心无出入一段。近偶得朱子说二条及先稿中一条。有若准备今日之语者。并录在别纸。未知高明更以为如何。幸赐反复。别纸
道夫言尝与子昂论心无出入。子昂谓心大无外。固无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与操之之故。非真有出入也。朱子曰言有出入。也是一个意思。言无出入。也是一个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无时。且看自家汩汩没没在这里。非出入而何。
按道夫说。正合盛论。而朱子此一段说。孔子自言有以辨非真有出入之说。
又曰出入便是存亡。有人言无出入。说得好。看来他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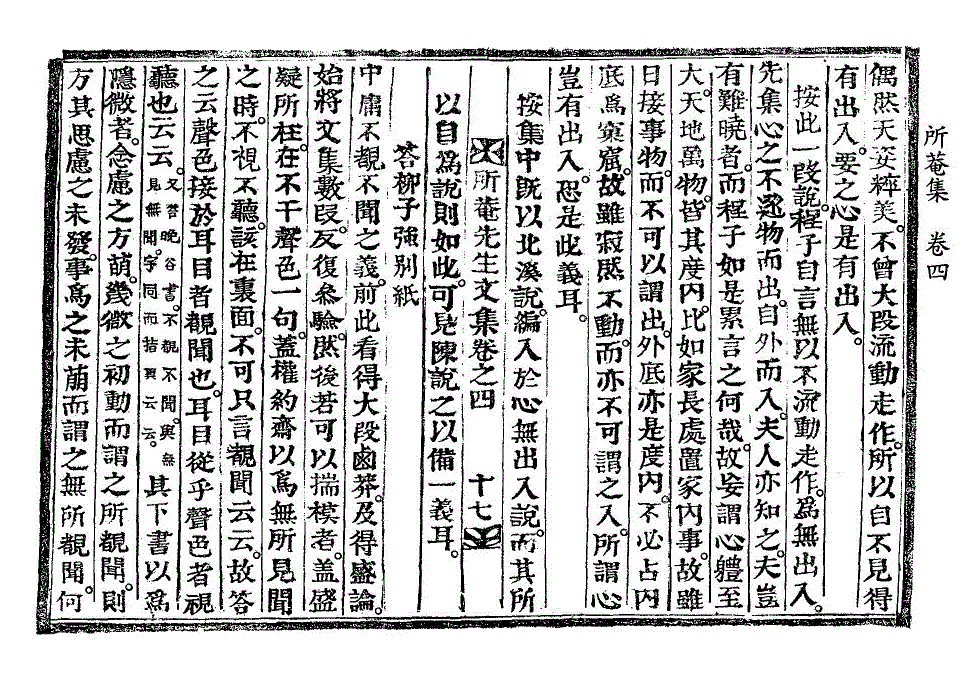 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动走作。所以自不见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
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动走作。所以自不见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按此一段说。程子自言无以不流动走作。为无出入。
先集心之不逐物而出。自外而入。夫人亦知之。夫岂有难晓者。而程子如是累言之何哉。故妄谓心体至大。天地万物。皆其度内。比如家长处置家内事。故虽日接事物。而不可以谓出。外底亦是度内。不必占内底为窠窟。故虽寂然不动。而亦不可谓之入。所谓心岂有出入。恐是此义耳。
按集中既以北溪说。编入于心无出入说。而其所以自为说则如此。可见陈说之以备一义耳。
答柳子强别纸
中庸不睹不闻之义。前此看得大段卤莽。及得盛论。始将文集数段。反复参验。然后若可以揣模者。盖盛疑所在。在不干声色一句。盖权约斋以为无所见闻之时。不视不听。该在里面。不可只言睹闻云云。故答之云声色接于耳目者睹闻也。耳目从乎声色者视听也云云。(又答晚谷书。不睹不闻。与无见无闻。字同而指异云云。)其下书以为隐微者。念虑之方萌。几微之初动而谓之所睹闻。则方其思虑之未发。事为之未萌而谓之无所睹闻。何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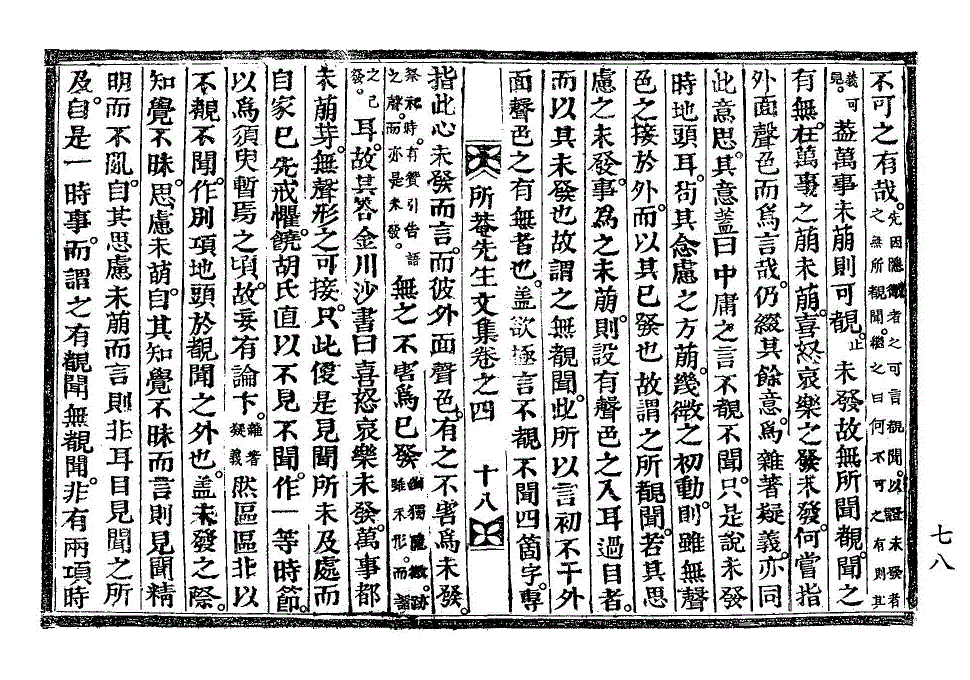 不可之有哉。(先因隐微者之可言睹闻。以證未发者之无所睹闻。继之曰何不可之有则其义可见。)盖万事未萌则可睹。(止)未发故无所闻睹。闻之有无。在万事之萌未萌。喜怒哀乐之发未发。何尝指外面声色而为言哉。仍缀其馀意。为杂著疑义。亦同此意思。其意盖曰中庸之言不睹不闻。只是说未发时地头耳。苟其念虑之方萌。几微之初动。则虽无声色之接于外。而以其已发也故谓之所睹闻。若其思虑之未发。事为之未萌。则设有声色之入耳过目者。而以其未发也故谓之无睹闻。此所以言初不干外面声色之有无者也。盖欲极言不睹不闻四个字。专指此心未发而言。而彼外面声色。有之不害为未发。(祭祀时。有赞引告语之声。而亦是未发。)无之不害为已发(幽独隐微。迹虽未形。而谓之已发。)耳。故其答金川沙书曰喜怒哀乐未发。万事都未萌芽。无声形之可接。只此便是见闻所未及处而自家已先戒惧。饶胡氏直以不见不闻。作一等时节。以为须臾暂焉之顷。故妄有论卞。(杂著疑义)然区区非以不睹不闻。作别项地头于睹闻之外也。盖未发之际。知觉不昧。思虑未萌。自其知觉不昧而言则见闻精明而不乱。自其思虑未萌而言则非耳目见闻之所及。自是一时事。而谓之有睹闻无睹闻。非有两项时
不可之有哉。(先因隐微者之可言睹闻。以證未发者之无所睹闻。继之曰何不可之有则其义可见。)盖万事未萌则可睹。(止)未发故无所闻睹。闻之有无。在万事之萌未萌。喜怒哀乐之发未发。何尝指外面声色而为言哉。仍缀其馀意。为杂著疑义。亦同此意思。其意盖曰中庸之言不睹不闻。只是说未发时地头耳。苟其念虑之方萌。几微之初动。则虽无声色之接于外。而以其已发也故谓之所睹闻。若其思虑之未发。事为之未萌。则设有声色之入耳过目者。而以其未发也故谓之无睹闻。此所以言初不干外面声色之有无者也。盖欲极言不睹不闻四个字。专指此心未发而言。而彼外面声色。有之不害为未发。(祭祀时。有赞引告语之声。而亦是未发。)无之不害为已发(幽独隐微。迹虽未形。而谓之已发。)耳。故其答金川沙书曰喜怒哀乐未发。万事都未萌芽。无声形之可接。只此便是见闻所未及处而自家已先戒惧。饶胡氏直以不见不闻。作一等时节。以为须臾暂焉之顷。故妄有论卞。(杂著疑义)然区区非以不睹不闻。作别项地头于睹闻之外也。盖未发之际。知觉不昧。思虑未萌。自其知觉不昧而言则见闻精明而不乱。自其思虑未萌而言则非耳目见闻之所及。自是一时事。而谓之有睹闻无睹闻。非有两项时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H 页
 分地头也。但程朱门下。以外面声色接于耳目者为言。而此则以思虑未萌万事未眹者言。其所指各别。(子约无闻无见之说。涉于昏眛。故朱子以声色之接于耳目者为言。约斋视听该在之说。侵过已发。故文集以思未萌事未朕为言。此其所指之别。而其实即此声色之接于外而思虑之未萌。正是一时事。非有异也。)详此意语。以见闻精明。思虑未萌两下立说。则所谓见闻精明者。其非指声色而言者乎。即此见闻精明之时。而苟其思虑之未萌。则这便是未发。这便是不睹闻。此之谓一时事。此之谓非有两项时分地头。而又何声色之足干哉。且以来谕所疑诸条言之。其曰李先生之言不睹闻。就思虑未萌上说。又曰先生亦言万事之萌未萌。所谓万事。似亦包声色在其中。而其下云何尝指外面声色云云。盖以思虑之事在内。而声色之事在外也。然朱子既以事物未接。思虑未萌。兼言于未发。则偏主事物未接者。固倚于一边。而偏主思虑未萌者。独非倚于一边乎。盖以集中所论。为偏主思虑而遗却事物也。今考其答约斋书曰方其思虑之未发。事为之未萌。曰万事已萌则可睹。其答川沙书曰喜怒哀乐未发。万事都未萌芽。又曰此则以思虑未萌。万事未眹者言。其答晚谷书曰事物未接。思虑未萌。泯然无形声之验。曰皆指喜怒未
分地头也。但程朱门下。以外面声色接于耳目者为言。而此则以思虑未萌万事未眹者言。其所指各别。(子约无闻无见之说。涉于昏眛。故朱子以声色之接于耳目者为言。约斋视听该在之说。侵过已发。故文集以思未萌事未朕为言。此其所指之别。而其实即此声色之接于外而思虑之未萌。正是一时事。非有异也。)详此意语。以见闻精明。思虑未萌两下立说。则所谓见闻精明者。其非指声色而言者乎。即此见闻精明之时。而苟其思虑之未萌。则这便是未发。这便是不睹闻。此之谓一时事。此之谓非有两项时分地头。而又何声色之足干哉。且以来谕所疑诸条言之。其曰李先生之言不睹闻。就思虑未萌上说。又曰先生亦言万事之萌未萌。所谓万事。似亦包声色在其中。而其下云何尝指外面声色云云。盖以思虑之事在内。而声色之事在外也。然朱子既以事物未接。思虑未萌。兼言于未发。则偏主事物未接者。固倚于一边。而偏主思虑未萌者。独非倚于一边乎。盖以集中所论。为偏主思虑而遗却事物也。今考其答约斋书曰方其思虑之未发。事为之未萌。曰万事已萌则可睹。其答川沙书曰喜怒哀乐未发。万事都未萌芽。又曰此则以思虑未萌。万事未眹者言。其答晚谷书曰事物未接。思虑未萌。泯然无形声之验。曰皆指喜怒未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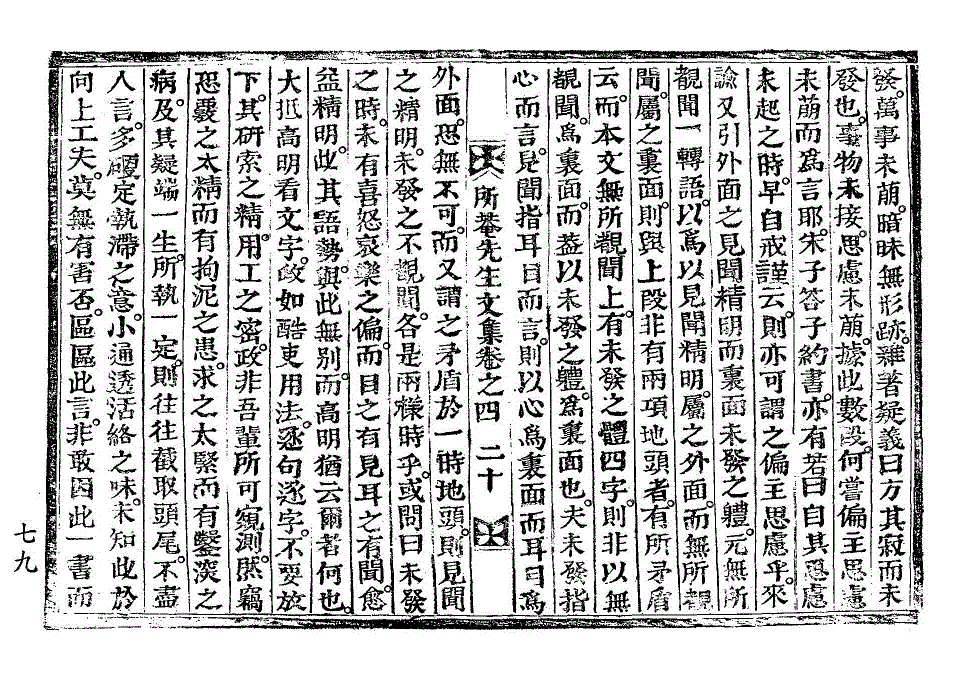 发。万事未萌。暗昧无形迹。杂著疑义曰方其寂而未发也。事物未接。思虑未萌。据此数段。何尝偏主思虑未萌而为言耶。朱子答子约书。亦有若曰自其思虑未起之时。早自戒谨云。则亦可谓之偏主思虑乎。来谕又引外面之见闻精明而里面未发之体。元无所睹闻一转语。以为以见闻精明。属之外面。而无所睹闻。属之里面。则与上段非有两项地头者。有所矛盾云。而本文无所睹闻上。有未发之体四字。则非以无睹闻。为里面。而盖以未发之体。为里面也。夫未发指心而言。见闻指耳目而言。则以心为里面而耳目为外面。恐无不可。而又谓之矛盾于一时地头。则见闻之精明。未发之不睹闻。各是两样时乎。或问曰未发之时。未有喜怒哀乐之偏。而目之有见耳之有闻。愈益精明。此其语势。与此无别。而高明犹云尔者何也。大抵高明看文字。政如酷吏用法。逐句逐字。不要放下。其研索之精。用工之密。政非吾辈所可窥测。然窃恐覈之太精而有拘泥之患。求之太紧而有凿深之病。及其疑端一生。所执一定。则往往截取头尾。不尽人言。多硬定执滞之意。小通透活络之味。未知此于向上工夫。莫无有害否。区区此言。非敢因此一书而
发。万事未萌。暗昧无形迹。杂著疑义曰方其寂而未发也。事物未接。思虑未萌。据此数段。何尝偏主思虑未萌而为言耶。朱子答子约书。亦有若曰自其思虑未起之时。早自戒谨云。则亦可谓之偏主思虑乎。来谕又引外面之见闻精明而里面未发之体。元无所睹闻一转语。以为以见闻精明。属之外面。而无所睹闻。属之里面。则与上段非有两项地头者。有所矛盾云。而本文无所睹闻上。有未发之体四字。则非以无睹闻。为里面。而盖以未发之体。为里面也。夫未发指心而言。见闻指耳目而言。则以心为里面而耳目为外面。恐无不可。而又谓之矛盾于一时地头。则见闻之精明。未发之不睹闻。各是两样时乎。或问曰未发之时。未有喜怒哀乐之偏。而目之有见耳之有闻。愈益精明。此其语势。与此无别。而高明犹云尔者何也。大抵高明看文字。政如酷吏用法。逐句逐字。不要放下。其研索之精。用工之密。政非吾辈所可窥测。然窃恐覈之太精而有拘泥之患。求之太紧而有凿深之病。及其疑端一生。所执一定。则往往截取头尾。不尽人言。多硬定执滞之意。小通透活络之味。未知此于向上工夫。莫无有害否。区区此言。非敢因此一书而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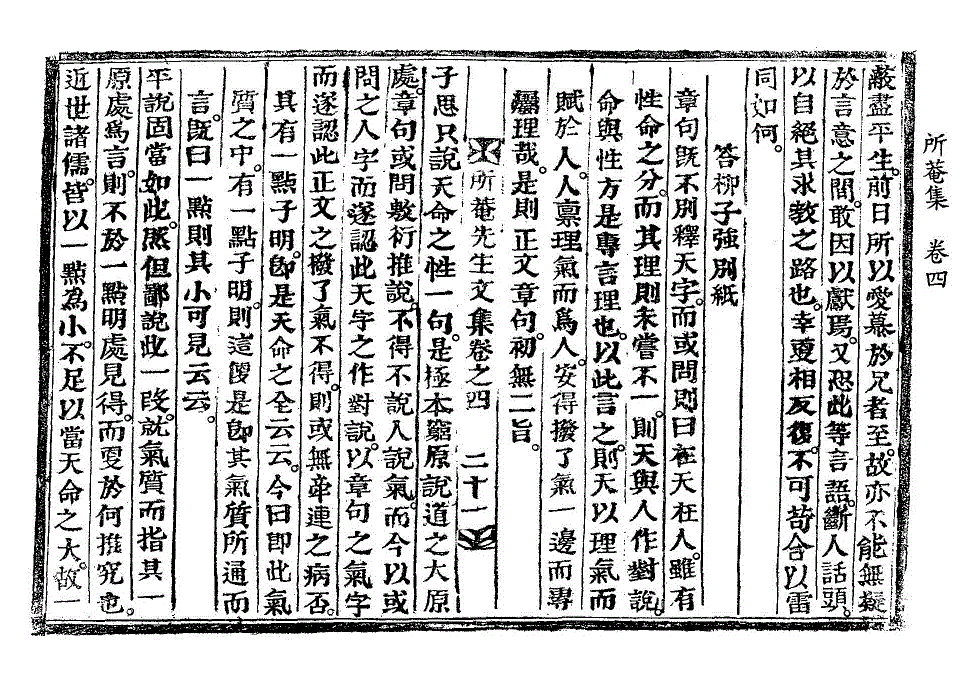 蔽尽平生。前日所以爱慕于兄者至。故亦不能无疑于言意之间。敢因以献焉。又恐此等言语。断人话头。以自绝其求教之路也。幸更相反复。不可苟合以雷同如何。
蔽尽平生。前日所以爱慕于兄者至。故亦不能无疑于言意之间。敢因以献焉。又恐此等言语。断人话头。以自绝其求教之路也。幸更相反复。不可苟合以雷同如何。答柳子强别纸
章句既不别释天字。而或问则曰在天在人。虽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则未尝不一。则天与人作对说。命与性方是专言理也。以此言之。则天以理气而赋于人。人禀理气而为人。安得拨了气一边而专属理哉。是则正文章句。初无二旨。
子思只说天命之性一句。是极本穷原说。道之大原处。章句或问敷衍推说。不得不说人说气。而今以或问之人字而遂认此天字之作对说。以章句之气字而遂认此正文之拨了气不得。则或无牵连之病否。
其有一点子明。即是天命之全云云。今曰即此气质之中。有一点子明。则这便是即其气质所通而言。既曰一点则其小可见云云。
平说固当如此。然但鄙说此一段。就气质而指其一原处为言。则不于一点明处见得。而更于何推究也。近世诸儒。皆以一点为小。不足以当天命之大。故一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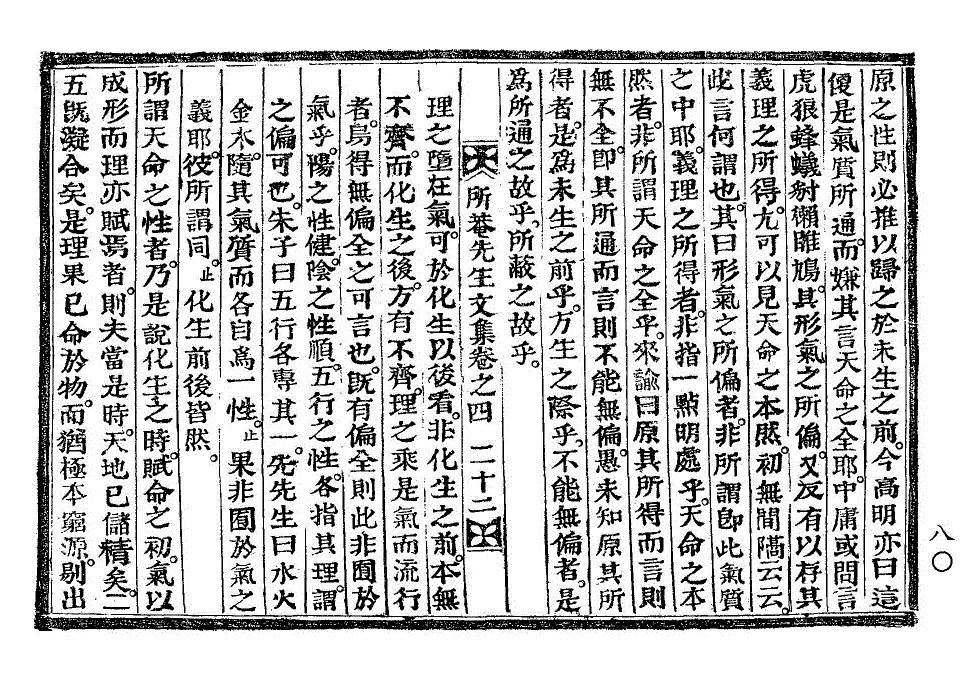 原之性则必推以归之于未生之前。今高明亦曰这便是气质所通。而嫌其言天命之全耶。中庸或问言虎狼蜂蚁豺獭雎鸠。其形气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义理之所得。尤可以见天命之本然。初无间隔云云。此言何谓也。其曰形气之所偏者。非所谓即此气质之中耶。义理之所得者。非指一点明处乎。天命之本然者。非所谓天命之全乎。来谕曰原其所得而言则无不全。即其所通而言则不能无偏。愚未知原其所得者。是为未生之前乎。方生之际乎。不能无偏者。是为所通之故乎。所蔽之故乎。
原之性则必推以归之于未生之前。今高明亦曰这便是气质所通。而嫌其言天命之全耶。中庸或问言虎狼蜂蚁豺獭雎鸠。其形气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义理之所得。尤可以见天命之本然。初无间隔云云。此言何谓也。其曰形气之所偏者。非所谓即此气质之中耶。义理之所得者。非指一点明处乎。天命之本然者。非所谓天命之全乎。来谕曰原其所得而言则无不全。即其所通而言则不能无偏。愚未知原其所得者。是为未生之前乎。方生之际乎。不能无偏者。是为所通之故乎。所蔽之故乎。理之堕在气。可于化生以后看。非化生之前。本无不齐。而化生之后。方有不齐。理之乘是气而流行者。乌得无偏全之可言也。既有偏全则此非囿于气乎。阳之性健。阴之性顺。五行之性。各指其理。谓之偏可也。朱子曰五行各专其一。先先生曰水火金木。随其气质而各自为一性。(止)果非囿于气之义耶。彼所谓同。(止)化生前后皆然。
所谓天命之性者。乃是说化生之时。赋命之初。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者。则夫当是时。天地已储精矣。二五既凝合矣。是理果已命于物。而犹极本穷源。剔出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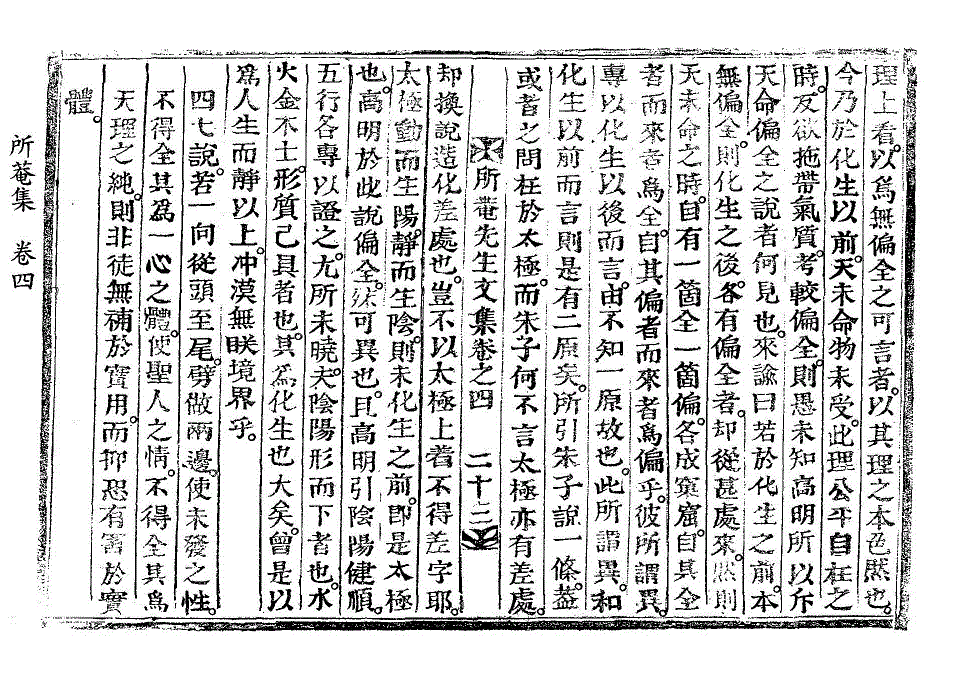 理上看。以为无偏全之可言者。以其理之本色然也。今乃于化生以前。天未命物未受。此理公平自在之时。反欲拖带气质。考较偏全。则愚未知高明所以斥天命偏全之说者何见也。来谕曰若于化生之前。本无偏全。则化生之后。各有偏全者。却从甚处来。然则天未命之时。自有一个全一个偏。各成窠窟。自其全者而来者为全。自其偏者而来者为偏乎。彼所谓异。专以化生以后而言。由不知一原故也。此所谓异。和化生以前而言则是有二原矣。所引朱子说一条。盖或者之问在于太极。而朱子何不言太极亦有差处。却换说造化差处也。岂不以太极上着不得差字耶。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未化生之前。即是太极也。高明于此说偏全。殊可异也。且高明引阴阳健顺。五行各专以證之。尤所未晓。夫阴阳形而下者也。水火金木土。形质已具者也。其为化生也大矣。曾是以为人生而静以上。冲漠无眹境界乎。
理上看。以为无偏全之可言者。以其理之本色然也。今乃于化生以前。天未命物未受。此理公平自在之时。反欲拖带气质。考较偏全。则愚未知高明所以斥天命偏全之说者何见也。来谕曰若于化生之前。本无偏全。则化生之后。各有偏全者。却从甚处来。然则天未命之时。自有一个全一个偏。各成窠窟。自其全者而来者为全。自其偏者而来者为偏乎。彼所谓异。专以化生以后而言。由不知一原故也。此所谓异。和化生以前而言则是有二原矣。所引朱子说一条。盖或者之问在于太极。而朱子何不言太极亦有差处。却换说造化差处也。岂不以太极上着不得差字耶。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未化生之前。即是太极也。高明于此说偏全。殊可异也。且高明引阴阳健顺。五行各专以證之。尤所未晓。夫阴阳形而下者也。水火金木土。形质已具者也。其为化生也大矣。曾是以为人生而静以上。冲漠无眹境界乎。四七说。若一向从头至尾。劈做两边。使未发之性。不得全其为一心之体。使圣人之情。不得全其为天理之纯。则非徒无补于实用。而抑恐有害于实体。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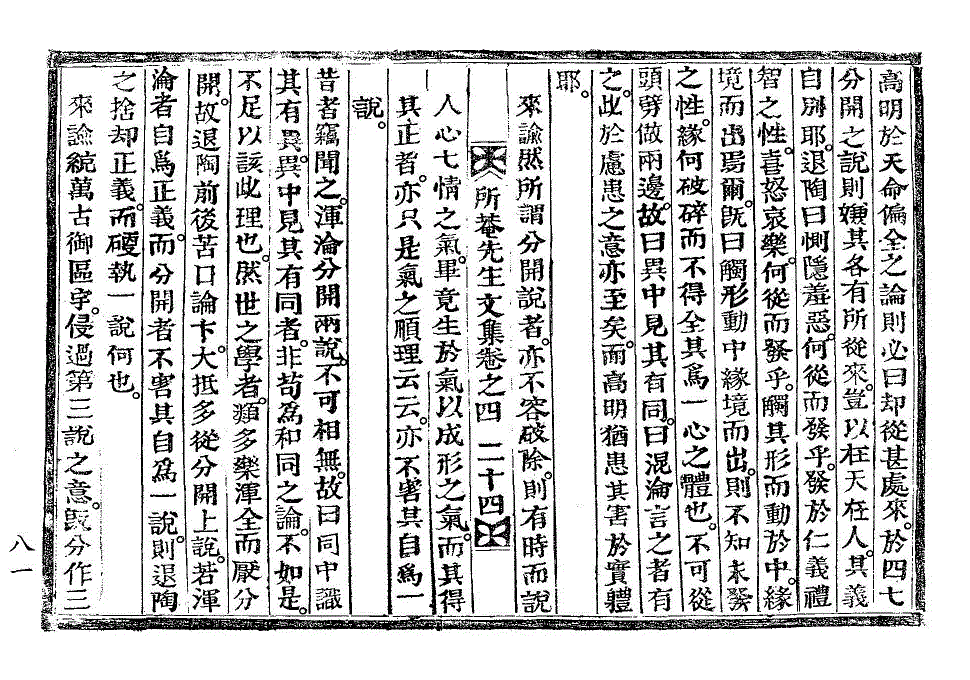 高明于天命偏全之论则必曰却从甚处来。于四七分开之说则嫌其各有所从来。岂以在天在人。其义自别耶。退陶曰恻隐羞恶。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乐。何从而发乎。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既曰触形动中缘境而出。则不知未发之性。缘何破碎而不得全其为一心之体也。不可从头劈做两边。故曰异中见其有同。曰混沦言之者有之。此于虑患之意亦至矣。而高明犹患其害于实体耶。
高明于天命偏全之论则必曰却从甚处来。于四七分开之说则嫌其各有所从来。岂以在天在人。其义自别耶。退陶曰恻隐羞恶。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乐。何从而发乎。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既曰触形动中缘境而出。则不知未发之性。缘何破碎而不得全其为一心之体也。不可从头劈做两边。故曰异中见其有同。曰混沦言之者有之。此于虑患之意亦至矣。而高明犹患其害于实体耶。来谕然所谓分开说者。亦不容破除。则有时而说人心七情之气。毕竟生于气以成形之气。而其得其正者。亦只是气之顺理云云。亦不害其自为一说。
昔者窃闻之。浑沦分开两说。不可相无。故曰同中识其有异。异中见其有同者。非苟为和同之论。不如是。不足以该此理也。然世之学者。类多乐浑全而厌分开。故退陶前后苦口论卞。大抵多从分开上说。若浑沦者自为正义。而分开者不害其自为一说。则退陶之舍却正义。而硬执一说何也。
来谕统万古御区宇。侵过第三说之意。既分作三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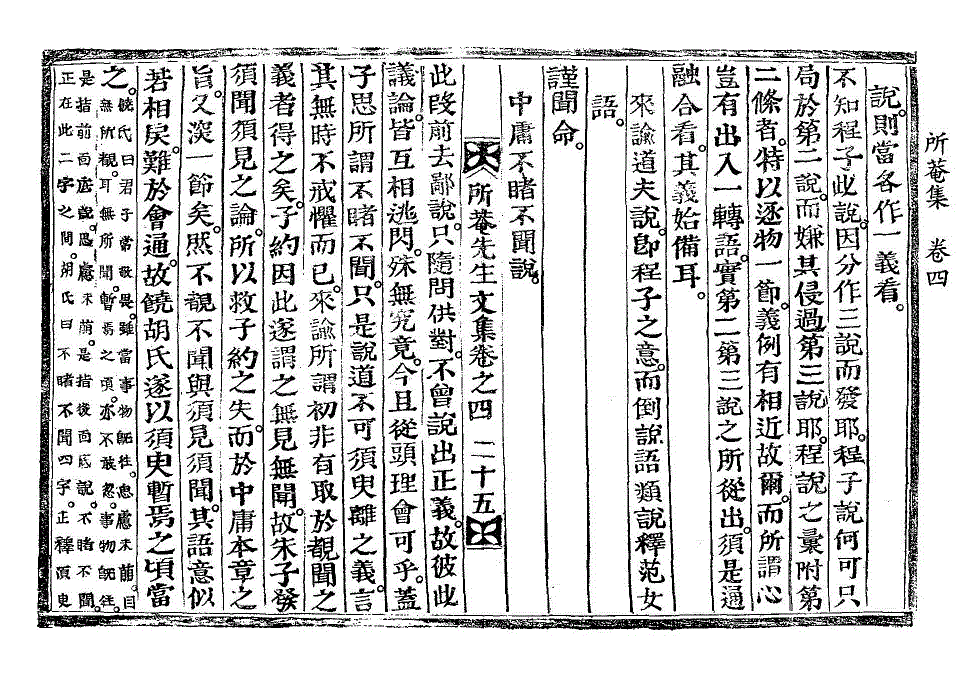 说。则当各作一义看。
说。则当各作一义看。不知程子此说。因分作三说而发耶。程子说何可只局于第二说。而嫌其侵过第三说耶。程说之汇附第二条者。特以逐物一节。义例有相近故尔。而所谓心岂有出入一转语。实第二第三说之所从出。须是通融合看。其义始备耳。
来谕道夫说。即程子之意。而倒说语类说释范女语。
谨闻命。
中庸不睹不闻说。
此段前去鄙说。只随问供对。不曾说出正义。故彼此议论。皆互相逃闪。殊无究竟。今且从头理会可乎。盖子思所谓不睹不闻。只是说道不可须臾离之义。言其无时不戒惧而已。来谕所谓初非有取于睹闻之义者得之矣。子约因此遂谓之无见无闻。故朱子发须闻须见之论。所以救子约之失。而于中庸本章之旨。又深一节矣。然不睹不闻与须见须闻。其语意似若相戾。难于会通。故饶胡氏遂以须臾暂焉之顷当之。(饶氏曰君子常敬畏。虽当事物既往。思虑未萌。目无所睹。耳无所闻。暂焉之顷。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说。思虑未萌。是指后面底说。不睹不闻。正在此二字之间。胡氏曰不睹不闻四字。正释须臾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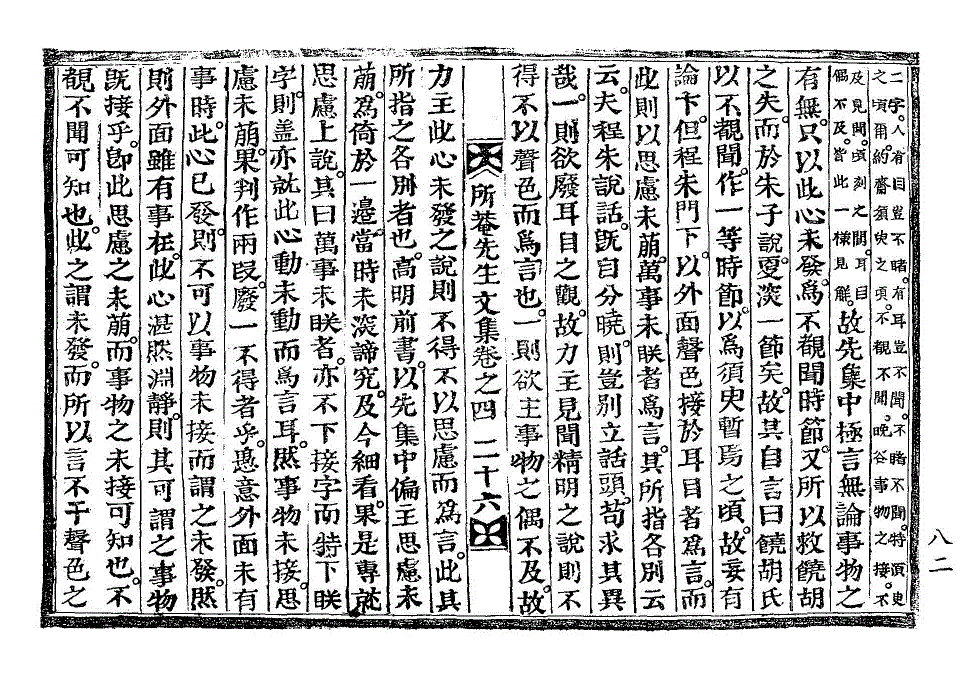 二字。人有目岂不睹。有耳岂不闻。不睹不闻。特须臾之顷尔。约斋须臾之顷。不睹不闻。晚谷事物之接。不及见闻。顷刻之间。耳目偶不及。皆此一样见解。)故先集中极言无论事物之有无。只以此心未发。为不睹闻时节。又所以救饶胡之失。而于朱子说。更深一节矣。故其自言曰饶胡氏以不睹闻。作一等时节。以为须臾暂焉之顷。故妄有论卞。但程朱门下。以外面声色接于耳目者为言。而此则以思虑未萌。万事未眹者为言。其所指各别云云。夫程朱说话。既自分晓。则岂别立话头。苟求其异哉。一则欲废耳目之观。故力主见闻精明之说则不得不以声色而为言也。一则欲主事物之偶不及。故力主此心未发之说则不得不以思虑而为言。此其所指之各别者也。高明前书。以先集中偏主思虑未萌。为倚于一边。当时未深谛究。及今细看。果是专就思虑上说。其曰万事未眹者。亦不下接字而特下眹字。则盖亦就此心动未动而为言耳。然事物未接。思虑未萌。果判作两段。废一不得者乎。愚意外面未有事时。此心已发。则不可以事物未接而谓之未发。然则外面虽有事在。此心湛然渊静。则其可谓之事物既接乎。即此思虑之未萌。而事物之未接可知也。不睹不闻可知也。此之谓未发。而所以言不干声色之
二字。人有目岂不睹。有耳岂不闻。不睹不闻。特须臾之顷尔。约斋须臾之顷。不睹不闻。晚谷事物之接。不及见闻。顷刻之间。耳目偶不及。皆此一样见解。)故先集中极言无论事物之有无。只以此心未发。为不睹闻时节。又所以救饶胡之失。而于朱子说。更深一节矣。故其自言曰饶胡氏以不睹闻。作一等时节。以为须臾暂焉之顷。故妄有论卞。但程朱门下。以外面声色接于耳目者为言。而此则以思虑未萌。万事未眹者为言。其所指各别云云。夫程朱说话。既自分晓。则岂别立话头。苟求其异哉。一则欲废耳目之观。故力主见闻精明之说则不得不以声色而为言也。一则欲主事物之偶不及。故力主此心未发之说则不得不以思虑而为言。此其所指之各别者也。高明前书。以先集中偏主思虑未萌。为倚于一边。当时未深谛究。及今细看。果是专就思虑上说。其曰万事未眹者。亦不下接字而特下眹字。则盖亦就此心动未动而为言耳。然事物未接。思虑未萌。果判作两段。废一不得者乎。愚意外面未有事时。此心已发。则不可以事物未接而谓之未发。然则外面虽有事在。此心湛然渊静。则其可谓之事物既接乎。即此思虑之未萌。而事物之未接可知也。不睹不闻可知也。此之谓未发。而所以言不干声色之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3H 页
 有无也。高明以为倚于一边。无乃过乎。但其语意。专就思虑上说。故段段提起此心寂然漠然无形影处。说不睹不闻之义。至一处直曰就未发时体段而言云云。则无怪乎高明之疑其以为心体之微。非耳目见闻所及也。然偶见后山记闻。问不睹不闻。看来就道上说。下文莫见莫显。亦以道之见显言之。似为相应。答曰饶双峰以道言之。固为非是。盖隐微以事而言。道固显于此。然是言隐微之事。正见显也云云。既以见显为非指道。则何可以不睹闻者。为指心体耶。鄙前书不能觑破高明发疑处。致有许多纷纭。此处合则馀可迎刃。故来录姑不逐条仰复。幸更考究。如有未当。却以反复如何。
有无也。高明以为倚于一边。无乃过乎。但其语意。专就思虑上说。故段段提起此心寂然漠然无形影处。说不睹不闻之义。至一处直曰就未发时体段而言云云。则无怪乎高明之疑其以为心体之微。非耳目见闻所及也。然偶见后山记闻。问不睹不闻。看来就道上说。下文莫见莫显。亦以道之见显言之。似为相应。答曰饶双峰以道言之。固为非是。盖隐微以事而言。道固显于此。然是言隐微之事。正见显也云云。既以见显为非指道。则何可以不睹闻者。为指心体耶。鄙前书不能觑破高明发疑处。致有许多纷纭。此处合则馀可迎刃。故来录姑不逐条仰复。幸更考究。如有未当。却以反复如何。答柳子强别纸
理与气。元不相离。阙一则便生物不得故也。
阙一则便生物不得故之故字。微有语病。理气元不相离。非为其生物之故而不相离也。
或问中未尝不包偏全之旨云云。
鄙说亦未尝不包偏全。如曰气质所通。如曰就气质而指其一原云。则虽说所通之明一原之全。而其气质之偏则依然故在也。前书盛论以为既曰一点则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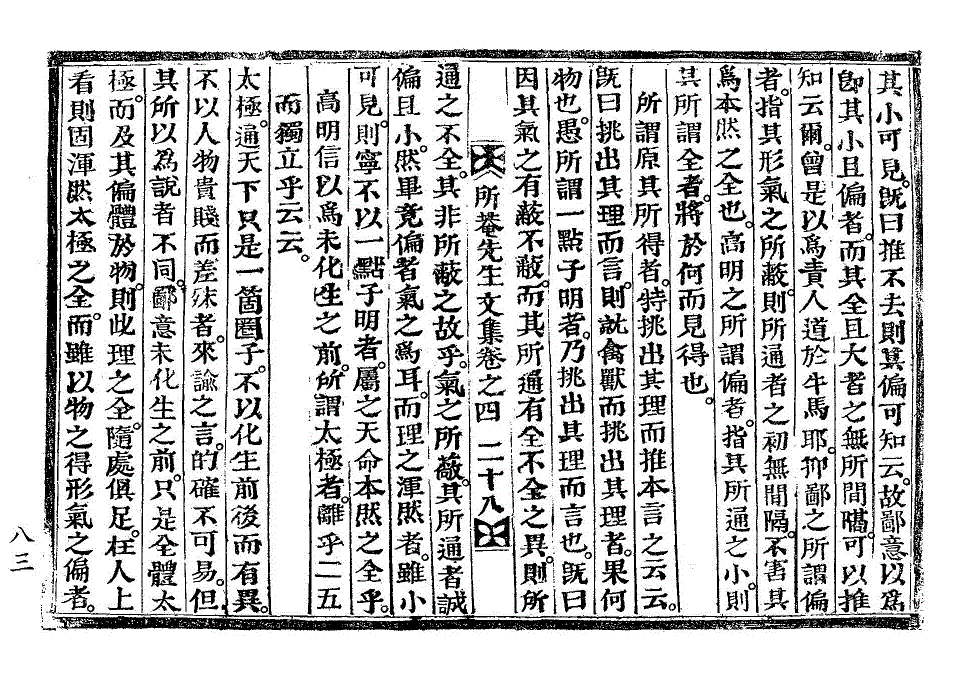 其小可见。既曰推不去则其偏可知云。故鄙意以为即其小且偏者。而其全且大者之无所间隔。可以推知云尔。曾是以为责人道于牛马耶。抑鄙之所谓偏者。指其形气之所蔽。则所通者之初无间隔。不害其为本然之全也。高明之所谓偏者。指其所通之小。则其所谓全者。将于何而见得也。
其小可见。既曰推不去则其偏可知云。故鄙意以为即其小且偏者。而其全且大者之无所间隔。可以推知云尔。曾是以为责人道于牛马耶。抑鄙之所谓偏者。指其形气之所蔽。则所通者之初无间隔。不害其为本然之全也。高明之所谓偏者。指其所通之小。则其所谓全者。将于何而见得也。所谓原其所得者。特挑出其理而推本言之云云。
既曰挑出其理而言。则就禽兽而挑出其理者。果何物也。愚所谓一点子明者。乃挑出其理而言也。既曰因其气之有蔽不蔽。而其所通有全不全之异。则所通之不全。其非所蔽之故乎。气之所蔽。其所通者诚偏且小。然毕竟偏者气之为耳。而理之浑然者。虽小可见。则宁不以一点子明者。属之天命本然之全乎。
高明信以为未化生之前。所谓太极者。离乎二五而独立乎云云。
太极。通天下只是一个圈子。不以化生前后而有异。不以人物贵贱而差殊者。来谕之言。的确不可易。但其所以为说者不同。鄙意未化生之前。只是全体太极。而及其偏体于物。则此理之全。随处俱足。在人上看则固浑然太极之全。而虽以物之得形气之偏者。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4H 页
 而其所通之明则未始非太极本然之体也。至如高明所论则既化生。只是这个偏全。未化生。亦是这个偏全。偏太极全太极。乌在其一个圈子而无人物贵贱之差殊也。朱子所谓正且通。偏且塞者。则固亦就化生处气上说耳。而高明乃引之于未化生太极偏全之论。岂亦以为有正通底太极。有偏全底太极耶。就气上看。就理上看者。诚愚之所欲言。而高明发之。请复得以申言之。盖今日之论。即所谓就理上看者也。天命之在人与物者。其偏正通塞。何啻百千。而特以就理上看。故拨了形气。挑出理一边。谓无偏全之可言。则高明当日亦不以为不可。而拖出化生以前囿于气。不能无偏之论。则区区窃听莹焉。朱子曰须知未有此气。先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若论其偏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等话头。不一而足。未或有拖曳气质。兼说偏塞于大原头极至处。此愚所以妄有论列。而高明前后缴纷。愈出愈惑。见说挑出理者。则引带气者而攻之。见说本体之全者。则引偏言者而斥之。至其所以證未化生
而其所通之明则未始非太极本然之体也。至如高明所论则既化生。只是这个偏全。未化生。亦是这个偏全。偏太极全太极。乌在其一个圈子而无人物贵贱之差殊也。朱子所谓正且通。偏且塞者。则固亦就化生处气上说耳。而高明乃引之于未化生太极偏全之论。岂亦以为有正通底太极。有偏全底太极耶。就气上看。就理上看者。诚愚之所欲言。而高明发之。请复得以申言之。盖今日之论。即所谓就理上看者也。天命之在人与物者。其偏正通塞。何啻百千。而特以就理上看。故拨了形气。挑出理一边。谓无偏全之可言。则高明当日亦不以为不可。而拖出化生以前囿于气。不能无偏之论。则区区窃听莹焉。朱子曰须知未有此气。先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若论其偏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等话头。不一而足。未或有拖曳气质。兼说偏塞于大原头极至处。此愚所以妄有论列。而高明前后缴纷。愈出愈惑。见说挑出理者。则引带气者而攻之。见说本体之全者。则引偏言者而斥之。至其所以證未化生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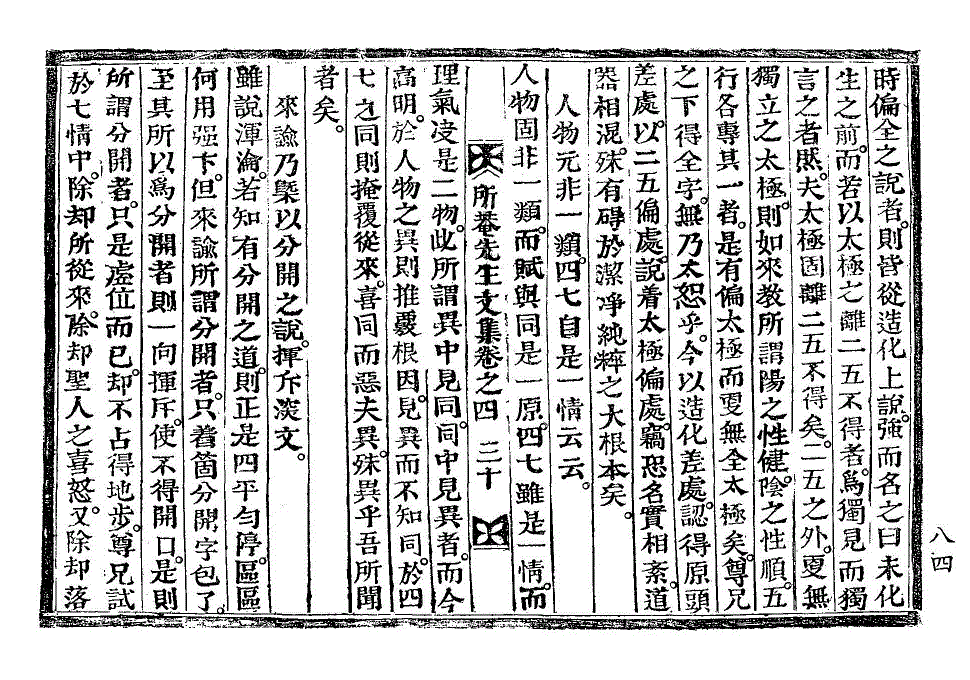 时偏全之说者。则皆从造化上说。强而名之曰未化生之前。而若以太极之离二五不得者。为独见而独言之者然。夫太极固离二五不得矣。二五之外。更无独立之太极。则如来教所谓阳之性健。阴之性顺。五行各专其一者。是有偏太极而更无全太极矣。尊兄之下得全字。无乃太恕乎。今以造化差处。认得原头差处。以二五偏处。说着太极偏处。窃恐名实相紊。道器相混。殊有碍于洁净纯粹之大根本矣。
时偏全之说者。则皆从造化上说。强而名之曰未化生之前。而若以太极之离二五不得者。为独见而独言之者然。夫太极固离二五不得矣。二五之外。更无独立之太极。则如来教所谓阳之性健。阴之性顺。五行各专其一者。是有偏太极而更无全太极矣。尊兄之下得全字。无乃太恕乎。今以造化差处。认得原头差处。以二五偏处。说着太极偏处。窃恐名实相紊。道器相混。殊有碍于洁净纯粹之大根本矣。人物元非一类。四七自是一情云云。
人物固非一类。而赋与同是一原。四七虽是一情。而理气决是二物。此所谓异中见同。同中见异者。而今高明。于人物之异则推覈根因。见异而不知同。于四七之同则掩覆从来。喜同而恶夫异。殊异乎吾所闻者矣。
来谕乃槩以分开之说。挥斥深文。
虽说浑沦。若知有分开之道。则正是四平匀停。区区何用强卞。但来谕所谓分开者。只着个分开字包了。至其所以为分开者则一向挥斥。使不得开口。是则所谓分开者。只是虚位而已。却不占得地步。尊兄试于七情中。除却所从来。除却圣人之喜怒。又除却落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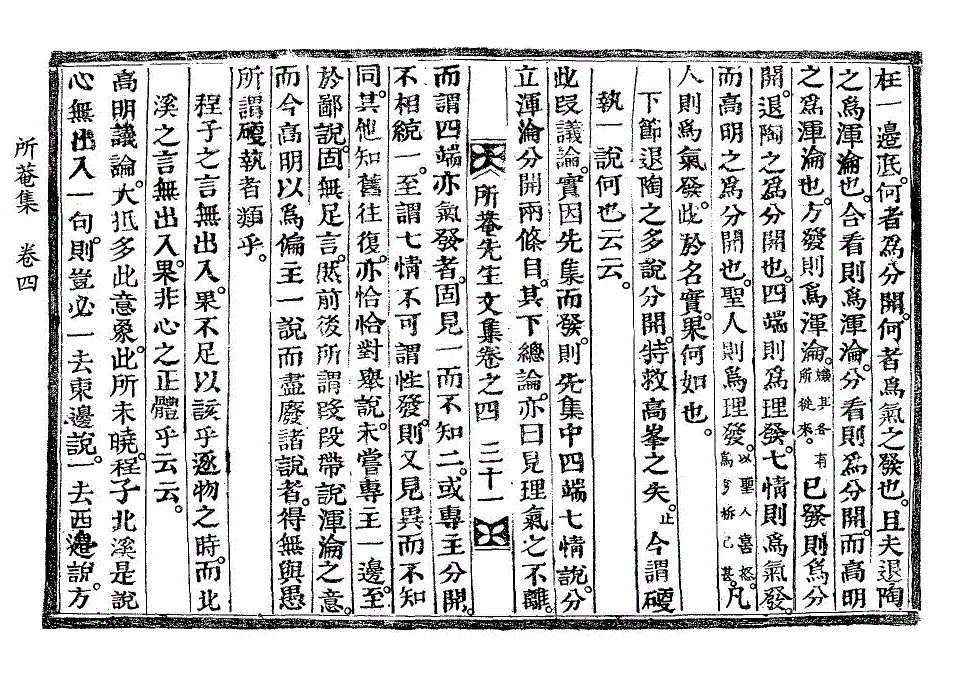 在一边底。何者为分开。何者为气之发也。且夫退陶之为浑沦也。合看则为浑沦。分看则为分开。而高明之为浑沦也。方发则为浑沦。(嫌其各有所从来。)已发则为分开。退陶之为分开也。四端则为理发。七情则为气发。而高明之为分开也。圣人则为理发。(以圣人喜怒。为分析已甚。)凡人则为气发。此于名实。果何如也。
在一边底。何者为分开。何者为气之发也。且夫退陶之为浑沦也。合看则为浑沦。分看则为分开。而高明之为浑沦也。方发则为浑沦。(嫌其各有所从来。)已发则为分开。退陶之为分开也。四端则为理发。七情则为气发。而高明之为分开也。圣人则为理发。(以圣人喜怒。为分析已甚。)凡人则为气发。此于名实。果何如也。下节退陶之多说分开。特救高峰之失。(止)今谓硬执一说何也云云。
此段议论。实因先集而发。则先集中四端七情说。分立浑沦分开两条目。其下总论。亦曰见理气之不离。而谓四端亦气发者。固见一而不知二。或专主分开。不相统一。至谓七情不可谓性发。则又见异而不知同。其他知旧往复。亦恰恰对举说。未尝专主一边。至于鄙说。固无足言。然前后所谓段段带说浑沦之意。而今高明以为偏主一说而尽废诸说者。得无与愚所谓硬执者类乎。
程子之言无出入。果不足以该乎逐物之时。而北溪之言无出入。果非心之正体乎云云。
高明议论。大抵多此意象。此所未晓。程子北溪是说心无出入一句。则岂必一去东边说。一去西边说。方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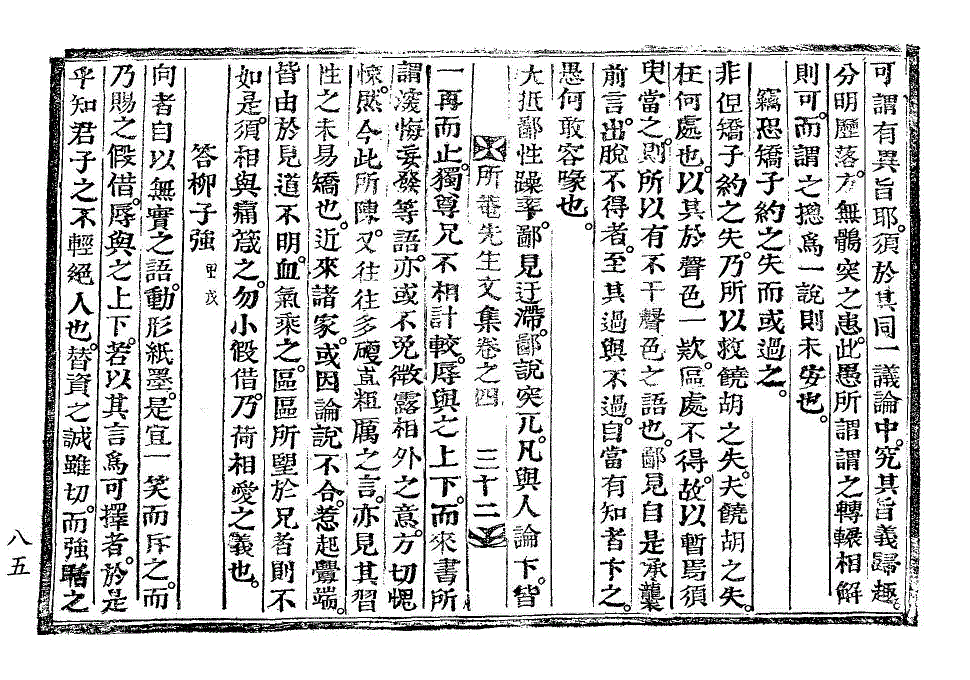 可谓有异旨耶。须于其同一议论中。究其旨义归趣。分明历落。方无体突之患。此愚所谓谓之转辗相解则可。而谓之总为一说则未安也。
可谓有异旨耶。须于其同一议论中。究其旨义归趣。分明历落。方无体突之患。此愚所谓谓之转辗相解则可。而谓之总为一说则未安也。窃恐矫子约之失而或过之。
非但矫子约之失。乃所以救饶胡之失。夫饶胡之失。在何处也。以其于声色一款。区处不得。故以暂焉须臾当之。则所以有不干声色之语也。鄙见自是承袭前言。出脱不得者。至其过与不过。自当有知者卞之。愚何敢容喙也。
大抵鄙性躁率。鄙见迂滞。鄙说突兀。凡与人论卞。皆一再而止。独尊兄不相计较。辱与之上下。而来书所谓深悔妄发等语。亦或不免微露相外之意。方切愧悚。然今此所陈。又往往多硬直粗厉之言。亦见其习性之未易矫也。近来诸家。或因论说不合。惹起衅端。皆由于见道不明。血气乘之。区区所望于兄者则不如是。须相与痛箴之。勿小假借。乃荷相爱之义也。
答柳子强(甲戌)
向者自以无实之语。动形纸墨。是宜一笑而斥之。而乃赐之假借。辱与之上下。若以其言为可择者。于是乎知君子之不轻绝人也。替资之诚虽切。而强聒之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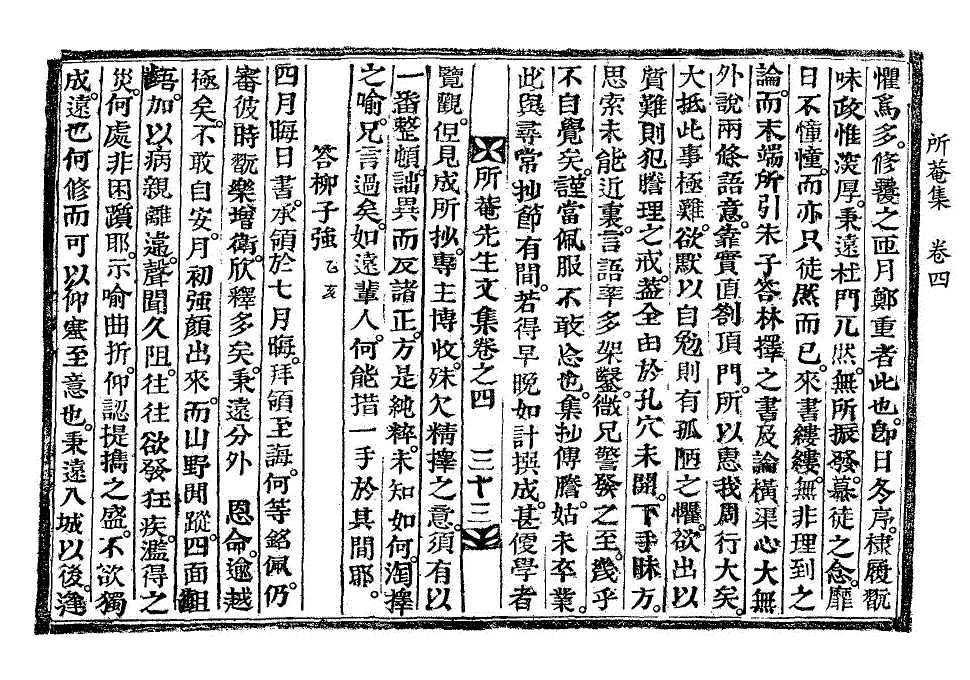 惧为多。修覆之匝月郑重者此也。即日冬序。棣履玩味政惟深厚。秉远杜门兀然。无所振发。慕徒之念。靡日不憧憧。而亦只徒然而已。来书缕缕。无非理到之论。而末端所引朱子答林择之书及论横渠心大无外说两条语意。靠实直劄顶门。所以惠我周行大矣。大抵此事极难。欲默以自勉则有孤陋之惧。欲出以质难则犯誊理之戒。盖全由于孔穴未开。下手昧方。思索未能近里。言语率多架凿。微兄警发之至。几乎不自觉矣。谨当佩服不敢忘也。集抄传誊。姑未卒业。此与寻常抄节有间。若得早晚如计撰成。甚便学者览观。但见成所抄。专主博收。殊欠精择之意。须有以一番整顿。诎异而反诸正。方是纯粹。未知如何。淘择之喻。兄言过矣。如远辈人。何能措一手于其间耶。
惧为多。修覆之匝月郑重者此也。即日冬序。棣履玩味政惟深厚。秉远杜门兀然。无所振发。慕徒之念。靡日不憧憧。而亦只徒然而已。来书缕缕。无非理到之论。而末端所引朱子答林择之书及论横渠心大无外说两条语意。靠实直劄顶门。所以惠我周行大矣。大抵此事极难。欲默以自勉则有孤陋之惧。欲出以质难则犯誊理之戒。盖全由于孔穴未开。下手昧方。思索未能近里。言语率多架凿。微兄警发之至。几乎不自觉矣。谨当佩服不敢忘也。集抄传誊。姑未卒业。此与寻常抄节有间。若得早晚如计撰成。甚便学者览观。但见成所抄。专主博收。殊欠精择之意。须有以一番整顿。诎异而反诸正。方是纯粹。未知如何。淘择之喻。兄言过矣。如远辈人。何能措一手于其间耶。答柳子强(乙亥)
四月晦日书。承领于七月晦。拜领至诲。何等铭佩。仍审彼时玩乐增卫。欣释多矣。秉远分外 恩命。逾越极矣。不敢自安。月初强颜出来。而山野閒踪。四面龃龉。加以病亲离违。声闻久阻。往往欲发狂疾。滥得之灾。何处非困踬耶。示喻曲折。仰认提携之盛。不欲独成。远也何修而可以仰塞至意也。秉远入城以后。逢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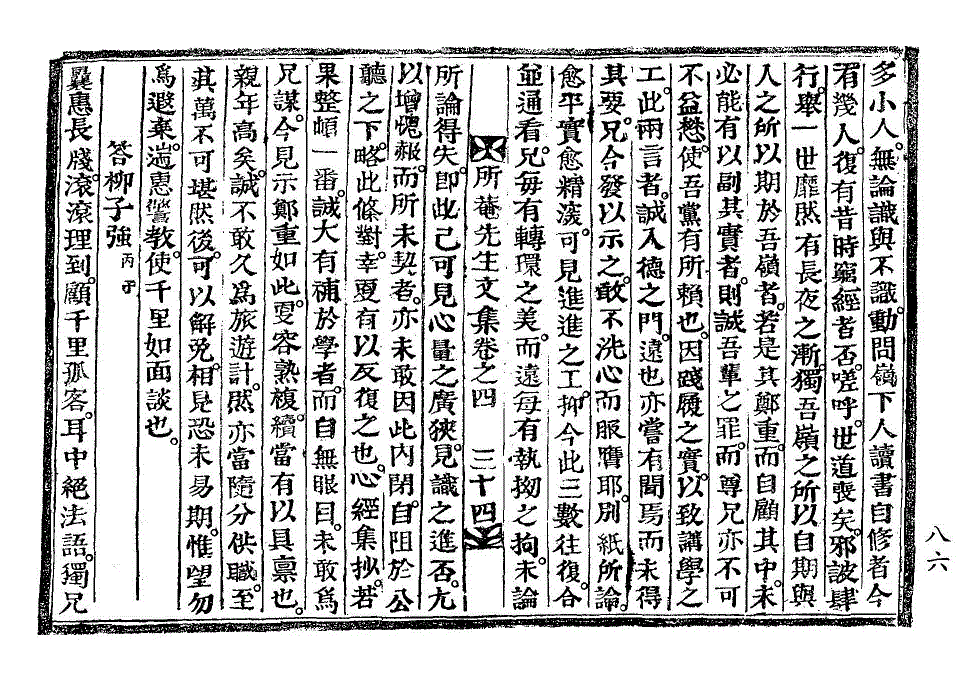 多小人。无论识与不识。动问岭下人读书自修者今有几人。复有昔时穷经者否。嗟呼。世道丧矣。邪诐肆行。举一世靡然有长夜之渐。独吾岭之所以自期与人之所以期于吾岭者。若是其郑重。而自顾其中。未必能有以副其实者。则诚吾辈之罪。而尊兄亦不可不益懋。使吾党有所赖也。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工。此两言者。诚入德之门。远也亦尝有闻焉而未得其要。兄今发以示之。敢不洗心而服膺耶。别纸所论。愈平实愈精深。可见进进之工。抑今此三数往复。合并通看。兄每有转环之美。而远每有执拗之拘。未论所论得失。即此已可见心量之广狭。见识之进否。尤以增愧赧。而所未契者。亦未敢因此内闭。自阻于公听之下。略此条对。幸更有以反复之也。心经集抄。若果整顿一番。诚大有补于学者。而自无眼目。未敢为兄谋。今见示郑重如此。更容熟复。续当有以具禀也。亲年高矣。诚不敢久为旅游计。然亦当随分供职。至其万不可堪然后。可以解免。相见恐未易期。惟望勿为遐弃。遄惠警教。使千里如面谈也。
多小人。无论识与不识。动问岭下人读书自修者今有几人。复有昔时穷经者否。嗟呼。世道丧矣。邪诐肆行。举一世靡然有长夜之渐。独吾岭之所以自期与人之所以期于吾岭者。若是其郑重。而自顾其中。未必能有以副其实者。则诚吾辈之罪。而尊兄亦不可不益懋。使吾党有所赖也。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工。此两言者。诚入德之门。远也亦尝有闻焉而未得其要。兄今发以示之。敢不洗心而服膺耶。别纸所论。愈平实愈精深。可见进进之工。抑今此三数往复。合并通看。兄每有转环之美。而远每有执拗之拘。未论所论得失。即此已可见心量之广狭。见识之进否。尤以增愧赧。而所未契者。亦未敢因此内闭。自阻于公听之下。略此条对。幸更有以反复之也。心经集抄。若果整顿一番。诚大有补于学者。而自无眼目。未敢为兄谋。今见示郑重如此。更容熟复。续当有以具禀也。亲年高矣。诚不敢久为旅游计。然亦当随分供职。至其万不可堪然后。可以解免。相见恐未易期。惟望勿为遐弃。遄惠警教。使千里如面谈也。答柳子强(丙子)
曩惠长笺。滚滚理到。顾千里孤客。耳中绝法语。独兄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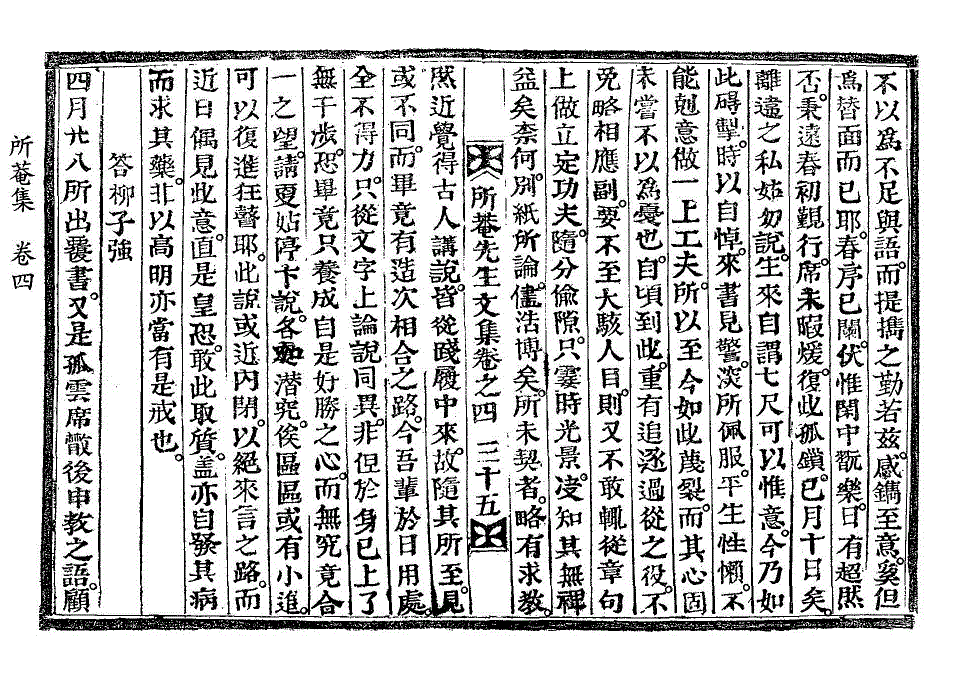 不以为不足与语。而提携之勤若玆。感镌至意。奚但为替面而已耶。春序已阑。伏惟闲中玩乐。日有超然否。秉远春初觐行。席未暇煖。复此孤锁。已月十日矣。离违之私姑勿说。生来自谓七尺可以惟意。今乃如此碍掣。时以自悼。来书见警。深所佩服。平生性懒。不能剋意做一上工夫。所以至今如此蔑裂。而其心固未尝不以为忧也。自顷到此。重有追逐过从之役。不免略相应副。要不至大骇人目。则又不敢辄从章句上做立定功夫。随分偷隙。只霎时光景。决知其无裨益矣柰何。别纸所论。尽浩博矣。所未契者。略有求教。然近觉得古人讲说。皆从践履中来。故随其所至。见或不同。而毕竟有造次相合之路。今吾辈于日用处。全不得力。只从文字上论说同异。非但于身己上了无干涉。恐毕竟只养成自是好胜之心。而无究竟合一之望。请更姑停卞说。各加潜究。俟区区或有小进。可以复进狂瞽耶。此说或近内闭。以绝来言之路。而近日偶见此意。直是皇恐。敢此取质。盖亦自发其病而求其药。非以高明亦当有是戒也。
不以为不足与语。而提携之勤若玆。感镌至意。奚但为替面而已耶。春序已阑。伏惟闲中玩乐。日有超然否。秉远春初觐行。席未暇煖。复此孤锁。已月十日矣。离违之私姑勿说。生来自谓七尺可以惟意。今乃如此碍掣。时以自悼。来书见警。深所佩服。平生性懒。不能剋意做一上工夫。所以至今如此蔑裂。而其心固未尝不以为忧也。自顷到此。重有追逐过从之役。不免略相应副。要不至大骇人目。则又不敢辄从章句上做立定功夫。随分偷隙。只霎时光景。决知其无裨益矣柰何。别纸所论。尽浩博矣。所未契者。略有求教。然近觉得古人讲说。皆从践履中来。故随其所至。见或不同。而毕竟有造次相合之路。今吾辈于日用处。全不得力。只从文字上论说同异。非但于身己上了无干涉。恐毕竟只养成自是好胜之心。而无究竟合一之望。请更姑停卞说。各加潜究。俟区区或有小进。可以复进狂瞽耶。此说或近内闭。以绝来言之路。而近日偶见此意。直是皇恐。敢此取质。盖亦自发其病而求其药。非以高明亦当有是戒也。答柳子强
四月廿八所出覆书。又是孤云席散后申教之语。顾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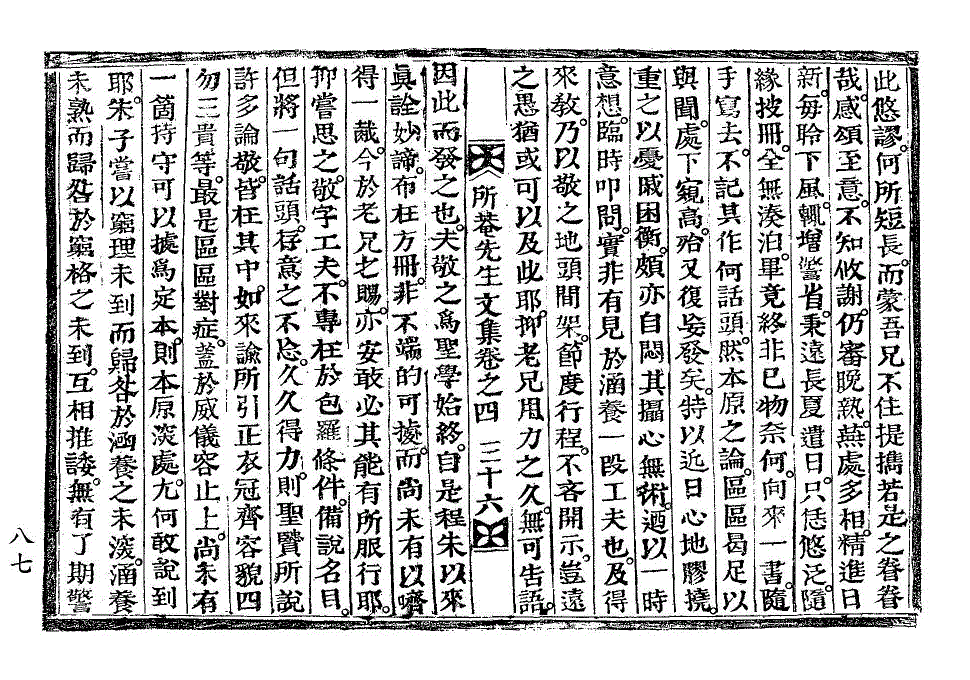 此悠谬。何所短长。而蒙吾兄不住提携若是之眷眷哉。感颂至意。不知攸谢。仍审晚热。燕处多相。精进日新。每聆下风。辄增警省。秉远长夏遣日。只恁悠泛。随缘披册。全无凑泊。毕竟终非己物奈何。向来一书。随手写去。不记其作何话头。然本原之论。区区曷足以与闻。处下窥高。殆又复妄发矣。特以近日心地胶挠。重之以忧戚困衡。颇亦自闷其摄心无术。乃以一时意想。临时叩问。实非有见于涵养一段工夫也。及得来教。乃以敬之地头间架。节度行程。不吝开示。岂远之愚犹或可以及此耶。抑老兄用力之久。无可告语。因此而发之也。夫敬之为圣学始终。自是程朱以来真诠妙谛。布在方册。非不端的可据。而尚未有以哜得一胾。今于老兄之赐。亦安敢必其能有所服行耶。抑尝思之。敬字工夫。不专在于包罗条件。备说名目。但将一句话头。存意之不忘。久久得力。则圣贤所说许多论敬。皆在其中。如来谕所引正衣冠齐容貌四勿三贵等。最是区区对症。盖于威仪容止上。尚未有一个持守可以据为定本。则本原深处。尤何敢说到耶。朱子尝以穷理未到而归咎于涵养之未深。涵养未熟而归咎于穷格之未到。互相推诿。无有了期警
此悠谬。何所短长。而蒙吾兄不住提携若是之眷眷哉。感颂至意。不知攸谢。仍审晚热。燕处多相。精进日新。每聆下风。辄增警省。秉远长夏遣日。只恁悠泛。随缘披册。全无凑泊。毕竟终非己物奈何。向来一书。随手写去。不记其作何话头。然本原之论。区区曷足以与闻。处下窥高。殆又复妄发矣。特以近日心地胶挠。重之以忧戚困衡。颇亦自闷其摄心无术。乃以一时意想。临时叩问。实非有见于涵养一段工夫也。及得来教。乃以敬之地头间架。节度行程。不吝开示。岂远之愚犹或可以及此耶。抑老兄用力之久。无可告语。因此而发之也。夫敬之为圣学始终。自是程朱以来真诠妙谛。布在方册。非不端的可据。而尚未有以哜得一胾。今于老兄之赐。亦安敢必其能有所服行耶。抑尝思之。敬字工夫。不专在于包罗条件。备说名目。但将一句话头。存意之不忘。久久得力。则圣贤所说许多论敬。皆在其中。如来谕所引正衣冠齐容貌四勿三贵等。最是区区对症。盖于威仪容止上。尚未有一个持守可以据为定本。则本原深处。尤何敢说到耶。朱子尝以穷理未到而归咎于涵养之未深。涵养未熟而归咎于穷格之未到。互相推诿。无有了期警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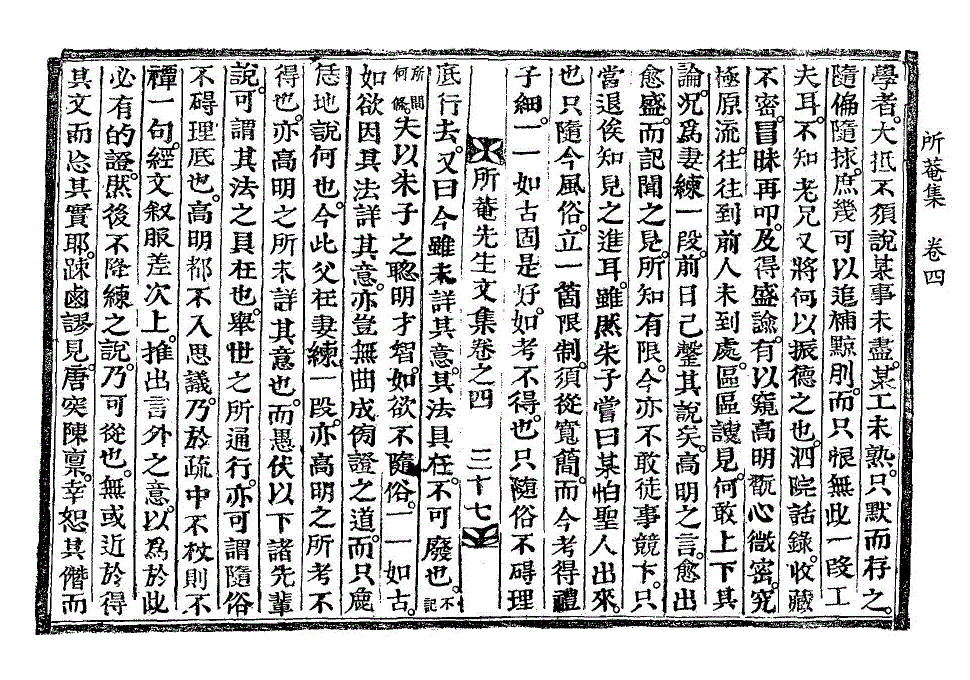 学者。大抵不须说某事未尽。某工未熟。只默而存之。随偏随救。庶几可以追补黥刖。而只恨无此一段工夫耳。不知老兄又将何以振德之也。泗院话录。收藏不密。冒昧再叩。及得盛谕。有以窥高明玩心微密。究极原流。往往到前人未到处。区区謏见。何敢上下其论。况为妻练一段。前日已罄其说矣。高明之言。愈出愈盛。而记闻之见。所知有限。今亦不敢徒事竞卞。只当退俟知见之进耳。虽然朱子尝曰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须从宽简。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随俗不碍理底行去。又曰今虽未详其意。其法具在。不可废也。(不记所问何条。)夫以朱子之聪明才智。如欲不随俗。一一如古。如欲因其法详其意。亦岂无曲成傍證之道。而只粗恁地说何也。今此父在妻练一段。亦高明之所考不得也。亦高明之所未详其意也。而愚伏以下诸先辈说。可谓其法之具在也。举世之所通行。亦可谓随俗不碍理底也。高明都不入思议。乃于疏中不杖则不禫一句。经文叙服差次上。推出言外之意。以为于此必有的證。然后不降练之说。乃可从也。无或近于得其文而忘其实耶。疏卤谬见。唐突陈禀。幸恕其僭而
学者。大抵不须说某事未尽。某工未熟。只默而存之。随偏随救。庶几可以追补黥刖。而只恨无此一段工夫耳。不知老兄又将何以振德之也。泗院话录。收藏不密。冒昧再叩。及得盛谕。有以窥高明玩心微密。究极原流。往往到前人未到处。区区謏见。何敢上下其论。况为妻练一段。前日已罄其说矣。高明之言。愈出愈盛。而记闻之见。所知有限。今亦不敢徒事竞卞。只当退俟知见之进耳。虽然朱子尝曰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须从宽简。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随俗不碍理底行去。又曰今虽未详其意。其法具在。不可废也。(不记所问何条。)夫以朱子之聪明才智。如欲不随俗。一一如古。如欲因其法详其意。亦岂无曲成傍證之道。而只粗恁地说何也。今此父在妻练一段。亦高明之所考不得也。亦高明之所未详其意也。而愚伏以下诸先辈说。可谓其法之具在也。举世之所通行。亦可谓随俗不碍理底也。高明都不入思议。乃于疏中不杖则不禫一句。经文叙服差次上。推出言外之意。以为于此必有的證。然后不降练之说。乃可从也。无或近于得其文而忘其实耶。疏卤谬见。唐突陈禀。幸恕其僭而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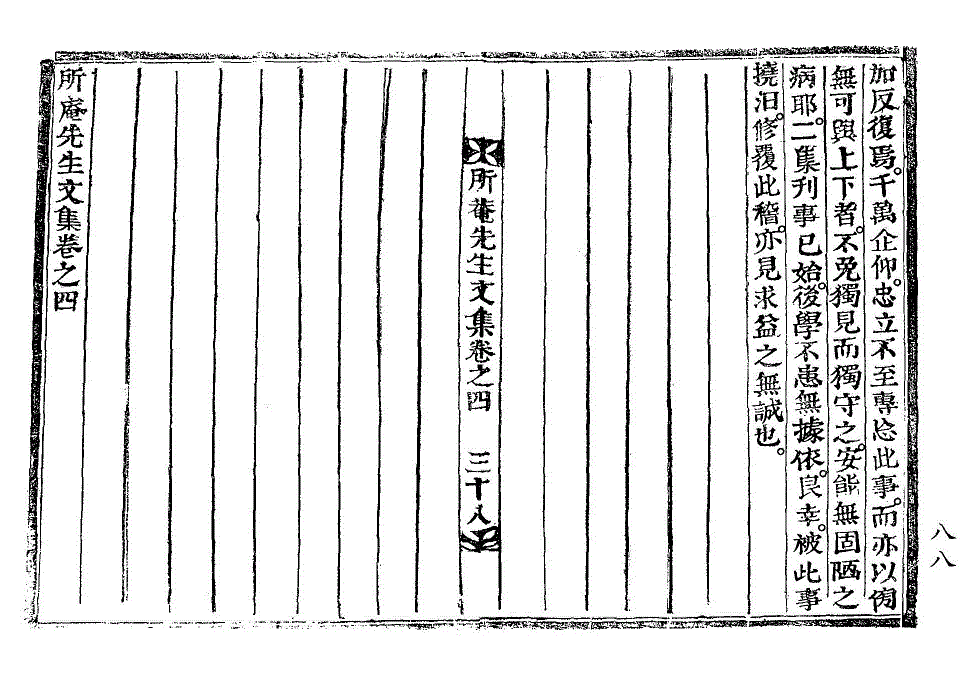 加反复焉。千万企仰。忠立不至专忘此事。而亦以傍无可与上下者。不免独见而独守之。安能无固陋之病耶。二集刊事已始。后学不患无据依。良幸。被此事挠汩。修覆此稽。亦见求益之无诚也。
加反复焉。千万企仰。忠立不至专忘此事。而亦以傍无可与上下者。不免独见而独守之。安能无固陋之病耶。二集刊事已始。后学不患无据依。良幸。被此事挠汩。修覆此稽。亦见求益之无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