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书
书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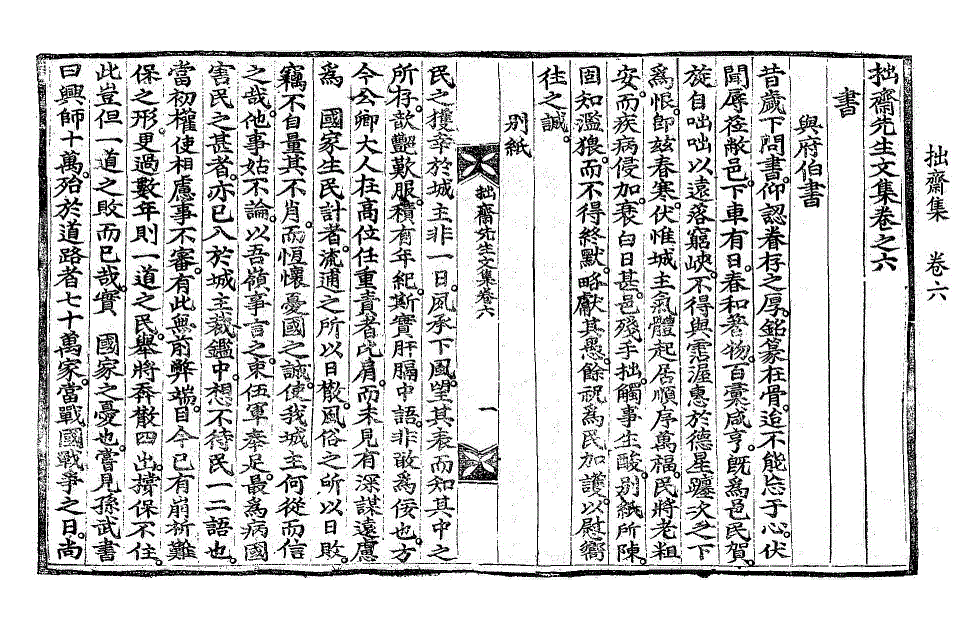 与府伯书
与府伯书昔岁下问书。仰认眷存之厚。铭篆在骨。迨不能忘于心。伏闻辱莅敝邑。下车有日。春和著物。百汇咸亨。既为邑民贺。旋自咄咄以远落穷峡。不得与沾渥惠于德星躔次之下为恨。即玆春寒。伏惟城主气体起居顺序万福。民将老粗安。而疾病侵加。衰白日甚。邑残手拙。触事生酸。别纸所陈。固知滥猥。而不得终默。略献其愚。馀祝为民加护。以慰向往之诚。
别纸
民之获幸于城主非一日。夙承下风。望其表而知其中之所存。歆艳叹服。积有年纪。斯实肝膈中语。非敢为佞也。方今公卿大人在高位任重责者比肩。而未见有深谋远虑为 国家生民计者。流逋之所以日散。风俗之所以日败。窃不自量其不肖。而恒怀忧国之诚。使我城主何从而信之哉。他事姑不论。以吾岭事言之。束伍军奉足。最为病国害民之甚者。亦已入于城主裁鉴中。想不待民一二语也。当初权使相虑事不审。有此无前弊端。目今已有崩析难保之形。更过数年则一道之民。举将奔散四出。撑保不住。此岂但一道之败而已哉。实 国家之忧也。尝见孙武书曰兴师十万。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当战国战争之日。尚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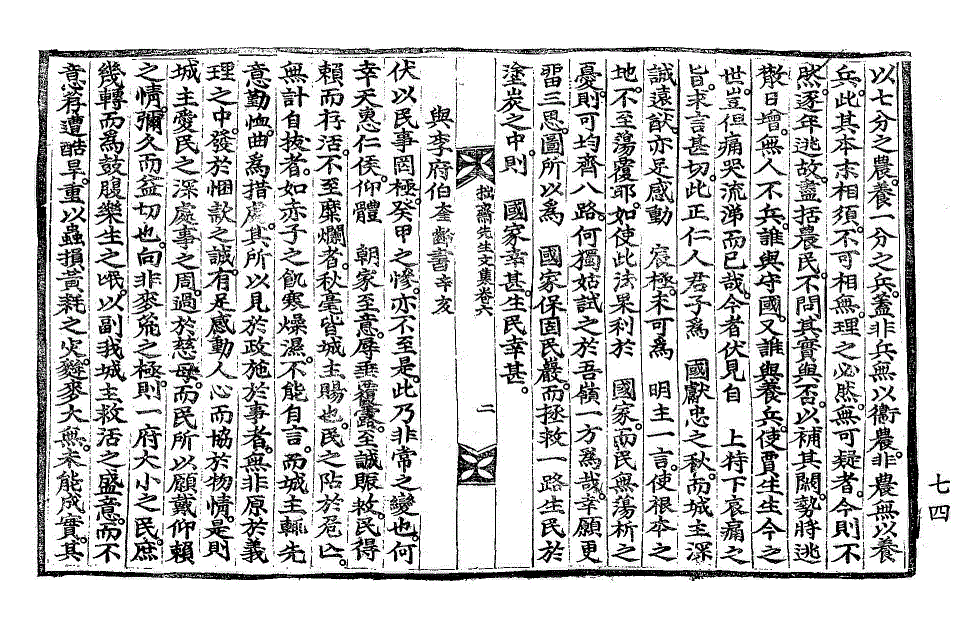 以七分之农。养一分之兵。盖非兵无以卫农。非农无以养兵。此其本末相须。不可相无。理之必然。无可疑者。今则不然。逐年逃故。尽括农民。不问其实与否。以补其阙。势将逃散日增。无人不兵。谁与守国。又谁与养兵。使贾生生今之世。岂但痛哭流涕而已哉。今者伏见自 上特下哀痛之旨。求言甚切。此正仁人君子为 国献忠之秋。而城主深诚远猷。亦足感动 宸极。未可为 明主一言。使根本之地。不至荡覆耶。如使此法果利于 国家。而民无荡析之忧。则可均齐八路。何独姑试之于吾岭一方为哉。幸愿更留三思。图所以为 国家保固民岩。而拯救一路生民于涂炭之中。则 国家幸甚。生民幸甚。
以七分之农。养一分之兵。盖非兵无以卫农。非农无以养兵。此其本末相须。不可相无。理之必然。无可疑者。今则不然。逐年逃故。尽括农民。不问其实与否。以补其阙。势将逃散日增。无人不兵。谁与守国。又谁与养兵。使贾生生今之世。岂但痛哭流涕而已哉。今者伏见自 上特下哀痛之旨。求言甚切。此正仁人君子为 国献忠之秋。而城主深诚远猷。亦足感动 宸极。未可为 明主一言。使根本之地。不至荡覆耶。如使此法果利于 国家。而民无荡析之忧。则可均齐八路。何独姑试之于吾岭一方为哉。幸愿更留三思。图所以为 国家保固民岩。而拯救一路生民于涂炭之中。则 国家幸甚。生民幸甚。与李府伯(奎龄)书(辛亥)
伏以民事罔极。癸甲之惨。亦不至是。此乃非常之变也。何幸天惠仁侯。仰体 朝家至意。辱垂覆露。至诚赈救。民得赖而存活。不至糜烂者。秋毫皆城主赐也。民之阽于危亡。无计自拔者。如赤子之饥寒燥湿。不能自言。而城主辄先意勤恤。曲为措处。其所以见于政施于事者。无非原于义理之中。发于悃款之诚。有足感动人心而协于物情。是则城主爱民之深处事之周。过于慈母。而民所以愿戴仰赖之情。弥久而益切也。向非麦荒之极。则一府大小之民。庶几转而为鼓腹乐生之氓。以副我城主救活之盛意。而不意荐遭酷旱。重以虫损黄耗之灾。麰麦大无。未能成实。其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5H 页
 细如针。又有草窃肆行之患。所收不及常年什之一二。其全不挂镰者。又什居八九。六月以后。道路之中。闾阎之间。僵尸之相枕。甚于春间。目今民间。所在空竭。比屋皆然。无论平日稍实与否。举皆涎沫俱尽。日就焦涸。岂知民生厄会之极。至于此乎。饥民之望哺。不啻什倍于春夏。而第念官中分赈之馀。仓储必少。未知城主何以救之耶。欲救则无粟。不救则立视其死。有以知城主衋然伤怀。怛然不宁。日夜焦劳。不能自释者。必万倍于往时矣。民之不肖。窃不自量。反覆筹思。粗有一得之愚。敢以为献。以备采择。伏愿城主幸垂裁察焉。
细如针。又有草窃肆行之患。所收不及常年什之一二。其全不挂镰者。又什居八九。六月以后。道路之中。闾阎之间。僵尸之相枕。甚于春间。目今民间。所在空竭。比屋皆然。无论平日稍实与否。举皆涎沫俱尽。日就焦涸。岂知民生厄会之极。至于此乎。饥民之望哺。不啻什倍于春夏。而第念官中分赈之馀。仓储必少。未知城主何以救之耶。欲救则无粟。不救则立视其死。有以知城主衋然伤怀。怛然不宁。日夜焦劳。不能自释者。必万倍于往时矣。民之不肖。窃不自量。反覆筹思。粗有一得之愚。敢以为献。以备采择。伏愿城主幸垂裁察焉。一曰粜籴分数捧上。盖救荒之难。虽无可奈何。而宽民一日之急。犹可以缓民一日之死。为今之计。莫如姑就捧籴。稍与之裁其阔狭。以救其沟壑滨死之命。此古人所谓催科中抚字。诚是不可不致力处也。今年春夏饥馑之馀。重以无前麦荒。流离颠仆而死者。遍于远近。设令有孑遗之民。或不尽灭。而六月以后。始得移秧。节晚之谷。难望有成。近又雨下不止。怪风又作。凡系害谷之灾。极备俱有。前头水沈霜损。风灾有无。又不可预料。且于其间。虽或有先种立苗之处。而势必尽于摘食。不待成熟。涂沫转急。馀力几何。积年还谷之未纳皆以此也。本府素称土瘠民贫。载于胜览。可考而知。虽在乐岁。每有艰食之患。况荐罹凶荒。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5L 页
 不能自存者乎。农事之失稔。有加于前秋。而生理艰难。又倍于春间。伏愿城主幸垂矜察。报于巡使。秋捧各谷。依上年例捧其三分之一。以济穷民之急。不胜幸甚。
不能自存者乎。农事之失稔。有加于前秋。而生理艰难。又倍于春间。伏愿城主幸垂矜察。报于巡使。秋捧各谷。依上年例捧其三分之一。以济穷民之急。不胜幸甚。二曰久远还谷之指徵无处者。不可不荡减。盖本府粜籴之弊。异于他邑。元会付各谷之外。又有各衙门谷物。一样分给于民间者。其数浩大。而以十馀年来。连岁被灾之故。结卜减缩。夫数不多。一户所受之多。至于百有馀石。民稀谷多之处。则厥数又倍。每年如此。旧者未纳而新粜又出。渐渐增加。驯致积滞未纳。因而逃亡者多。遂为指徵无处之物。民之重困。不得保存。实由于此。当此凶荒罔极之时。不得蒙荡涤悯恤之典。则亦何所仰赖以为得生之路哉。昔孔戣为广南观察使。蠲其负逋之缗钱数百馀万。耗金之州。困不得偿者亦尽除之。此皆民所应纳之物也。在古已行。今何独不然乎。诚愿城主以此转报。得以 启达。则厥今民生难保。而 圣朝之轸念方深。岂不 俯从所请。以副我城主之至悃哉。伏愿城主更加留意焉。
三曰未收还谷不出耗。上年自 朝家轸恤民隐。凡未收还谷。减其耗数。此体下如伤之至意也。今年失稔之极。无异于上年。前头民事之可忧。不啻寻常。伏愿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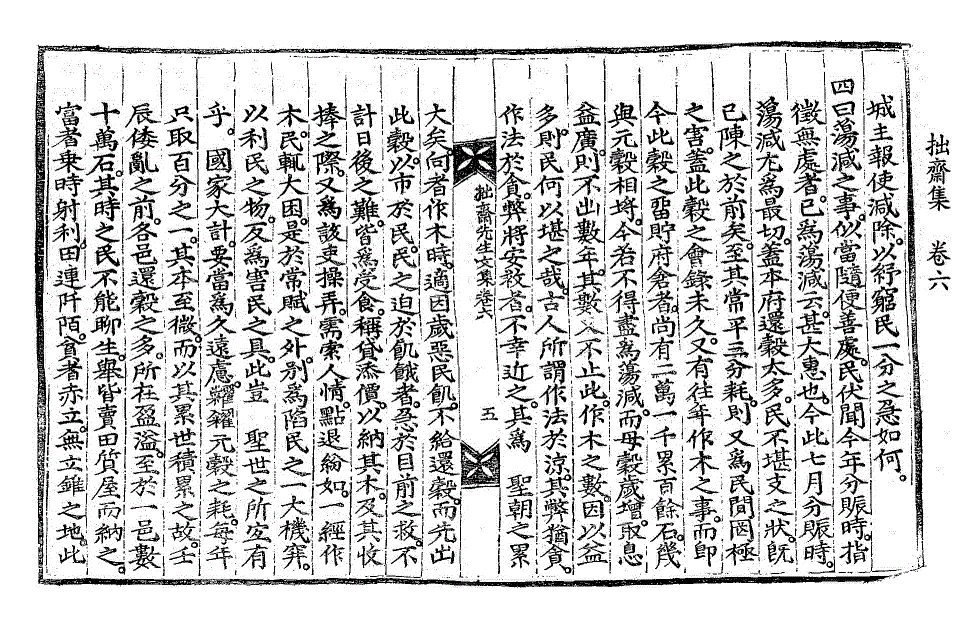 城主报使减除。以纾穷民一分之急如何。
城主报使减除。以纾穷民一分之急如何。四曰荡减之事。似当随便善处。民伏闻今年分赈时。指徵无处者。已为荡减云。甚大惠也。今此七月分赈时。荡减尤为最切。盖本府还谷太多。民不堪支之状。既已陈之于前矣。至其常平三分耗。则又为民间罔极之害。盖此谷之会录未久。又有往年作木之事。而即今此谷之留贮府仓者。尚有二万一千累百馀石。几与元谷相埒。今若不得尽为荡减。而母谷岁增。取息益广。则不出数年。其数又不止此。作木之数。因以益多。则民何以堪之哉。古人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者。不幸近之。其为 圣朝之累大矣。向者作木时。适因岁恶民饥。不给还谷。而先出此谷。以市于民。民之迫于饥饿者。急于目前之救。不计日后之难。皆为受食。称贷添价。以纳其木。及其收捧之际。又为该吏操弄。需索人情。点退纷如。一经作木。民辄大困。是于常赋之外。别为陷民之一大机阱。以利民之物。反为害民之具。此岂 圣世之所宜有乎。 国家大计。要当为久远虑。粜籴元谷之耗。每年只取百分之一。其本至微。而以其累世积累之故。壬辰倭乱之前。各邑还谷之多。所在盈溢。至于一邑数十万石。其时之民不能聊生。举皆卖田质屋而纳之。富者乘时射利。田连阡陌。贫者赤立。无立锥之地。此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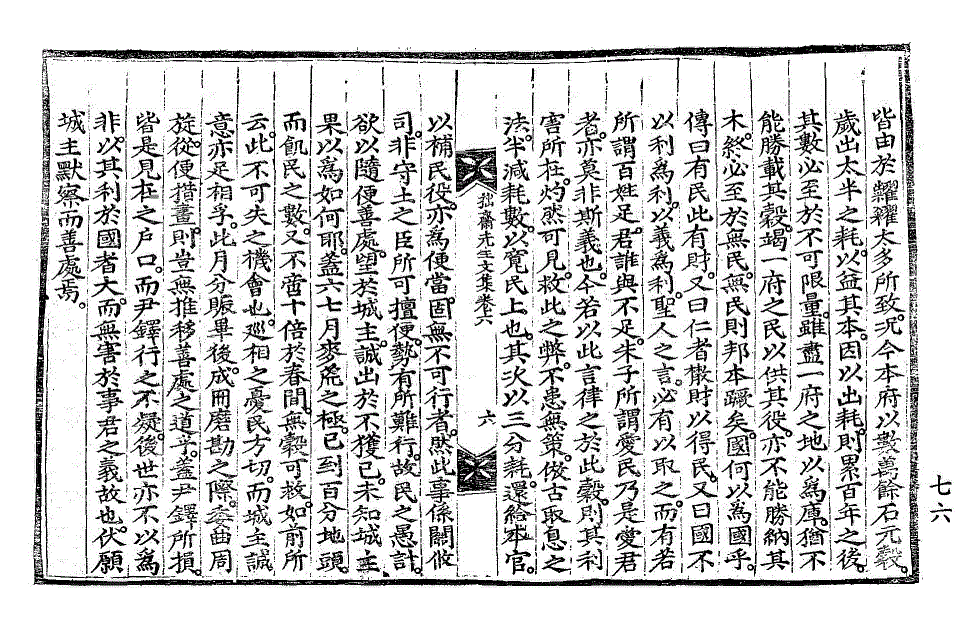 皆由于粜籴太多所致。况今本府以数万馀石元谷。岁出太半之耗。以益其本。因以出耗。则累百年之后。其数必至于不可限量。虽尽一府之地以为库。犹不能胜载其谷。竭一府之民以供其役。亦不能胜纳其木。终必至于无民。无民则邦本蹶矣。国何以为国乎。传曰有民此有财。又曰仁者散财以得民。又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圣人之言。必有以取之。而有若所谓百姓足。君谁与不足。朱子所谓爱民乃是爱君者。亦莫非斯义也。今若以此言律之于此谷。则其利害所在。灼然可见。救此之弊。不患无策。仿古取息之法。半减耗数。以宽民上也。其次以三分耗。还给本官。以补民役。亦为便当。固无不可行者。然此事系关攸司。非守土之臣所可擅便。势有所难行。故民之愚计。欲以随便善处。望于城主。诚出于不获已。未知城主果以为如何耶。盖六七月麦荒之极。已到百分地头。而饥民之数。又不啻十倍于春间。无谷可救。如前所云。此不可失之机会也。巡相之忧民方切。而城主诚意亦足相孚。此月分赈毕后。成册磨勘之际。委曲周旋。从便措画。则岂无推移善处之道乎。盖尹铎所损。皆是见在之户口。而尹铎行之不疑。后世亦不以为非。以其利于国者大。而无害于事君之义故也。伏愿城主默察而善处焉。
皆由于粜籴太多所致。况今本府以数万馀石元谷。岁出太半之耗。以益其本。因以出耗。则累百年之后。其数必至于不可限量。虽尽一府之地以为库。犹不能胜载其谷。竭一府之民以供其役。亦不能胜纳其木。终必至于无民。无民则邦本蹶矣。国何以为国乎。传曰有民此有财。又曰仁者散财以得民。又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圣人之言。必有以取之。而有若所谓百姓足。君谁与不足。朱子所谓爱民乃是爱君者。亦莫非斯义也。今若以此言律之于此谷。则其利害所在。灼然可见。救此之弊。不患无策。仿古取息之法。半减耗数。以宽民上也。其次以三分耗。还给本官。以补民役。亦为便当。固无不可行者。然此事系关攸司。非守土之臣所可擅便。势有所难行。故民之愚计。欲以随便善处。望于城主。诚出于不获已。未知城主果以为如何耶。盖六七月麦荒之极。已到百分地头。而饥民之数。又不啻十倍于春间。无谷可救。如前所云。此不可失之机会也。巡相之忧民方切。而城主诚意亦足相孚。此月分赈毕后。成册磨勘之际。委曲周旋。从便措画。则岂无推移善处之道乎。盖尹铎所损。皆是见在之户口。而尹铎行之不疑。后世亦不以为非。以其利于国者大。而无害于事君之义故也。伏愿城主默察而善处焉。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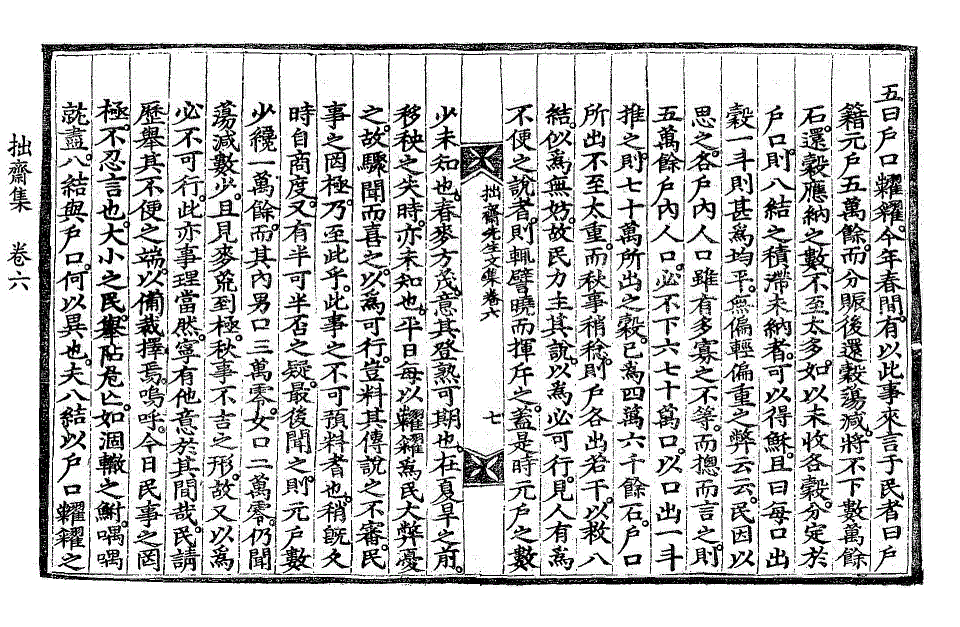 五曰户口粜籴。今年春间。有以此事来言于民者曰户籍元户五万馀。而分赈后还谷荡减。将不下数万馀石。还谷应纳之数。不至太多。如以未收各谷。分定于户口。则八结之积滞未纳者。可以得稣。且曰每口出谷一斗则甚为均平。无偏轻偏重之弊云云。民因以思之。各户内人口虽有多寡之不等。而总而言之。则五万馀户内人口。必不下六七十万口。以口出一斗推之。则七十万所出之谷。已为四万六千馀石。户口所出不至太重。而秋事稍稔。则户各出若干。以救八结。似为无妨。故民力主其说。以为必可行。见人有为不便之说者。则辄譬晓而挥斥之。盖是时元户之数少未知也。春麦方茂。意其登熟可期也。在夏旱之前。移秧之失时。亦未知也。平日每以粜籴为民大弊忧之。故骤闻而喜之。以为可行。岂料其传说之不审。民事之罔极。乃至此乎。此事之不可预料者也。稍既久时自商度。又有半可半否之疑。最后闻之。则元户数少才一万馀。而其内男口三万零。女口二万零。仍闻荡减数少。且见麦荒到极。秋事不吉之形。故又以为必不可行。此亦事理当然。宁有他意于其间哉。民请历举其不便之端。以备裁择焉。呜呼。今日民事之罔极。不忍言也。大小之民。举阽危亡。如涸辙之鲋。喁喁就尽。八结与户口。何以异也。夫八结以户口粜籴之
五曰户口粜籴。今年春间。有以此事来言于民者曰户籍元户五万馀。而分赈后还谷荡减。将不下数万馀石。还谷应纳之数。不至太多。如以未收各谷。分定于户口。则八结之积滞未纳者。可以得稣。且曰每口出谷一斗则甚为均平。无偏轻偏重之弊云云。民因以思之。各户内人口虽有多寡之不等。而总而言之。则五万馀户内人口。必不下六七十万口。以口出一斗推之。则七十万所出之谷。已为四万六千馀石。户口所出不至太重。而秋事稍稔。则户各出若干。以救八结。似为无妨。故民力主其说。以为必可行。见人有为不便之说者。则辄譬晓而挥斥之。盖是时元户之数少未知也。春麦方茂。意其登熟可期也。在夏旱之前。移秧之失时。亦未知也。平日每以粜籴为民大弊忧之。故骤闻而喜之。以为可行。岂料其传说之不审。民事之罔极。乃至此乎。此事之不可预料者也。稍既久时自商度。又有半可半否之疑。最后闻之。则元户数少才一万馀。而其内男口三万零。女口二万零。仍闻荡减数少。且见麦荒到极。秋事不吉之形。故又以为必不可行。此亦事理当然。宁有他意于其间哉。民请历举其不便之端。以备裁择焉。呜呼。今日民事之罔极。不忍言也。大小之民。举阽危亡。如涸辙之鲋。喁喁就尽。八结与户口。何以异也。夫八结以户口粜籴之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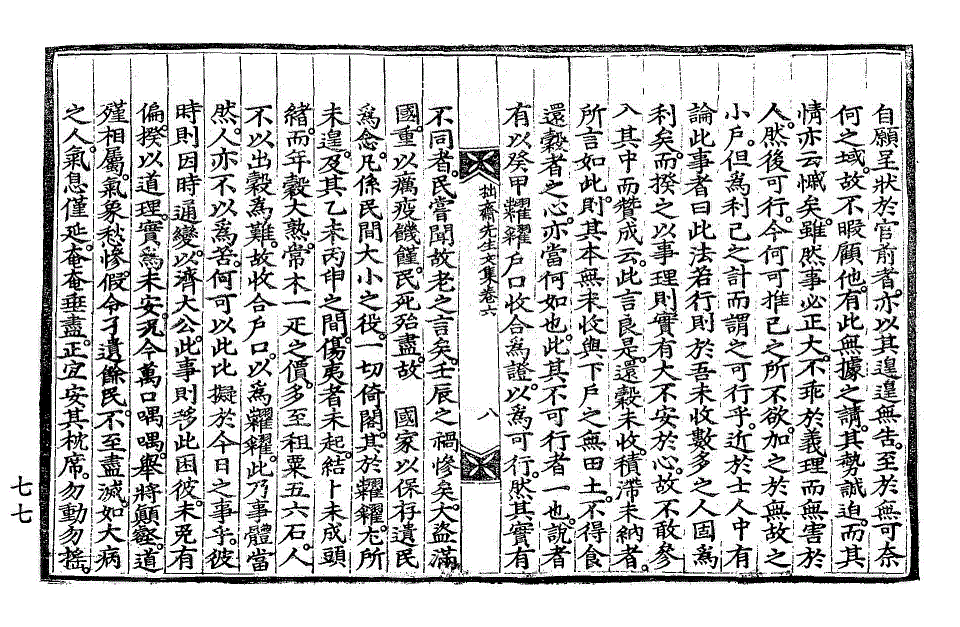 自愿呈状于官前者。亦以其遑遑无告。至于无可奈何之域。故不暇顾他。有此无据之请。其势诚迫。而其情亦云戚矣。虽然事必正大。不乖于义理而无害于人。然后可行。今何可推己之所不欲。加之于无故之小户。但为利己之计而谓之可行乎。近于士人中有论此事者曰此法若行则于吾未收数多之人固为利矣。而揆之以事理则实有大不安于心。故不敢参入其中而赞成云。此言良是。还谷未收。积滞未纳者。所言如此。则其本无未收与下户之无田土。不得食还谷者之心。亦当何如也。此其不可行者一也。说者有以癸甲粜籴户口收合为證。以为可行。然其实有不同者。民尝闻故老之言矣。壬辰之祸惨矣。大盗满国。重以疠疫饥馑。民死殆尽。故 国家以保存遗民为念。凡系民间大小之役。一切倚阁。其于粜籴。尤所未遑。及其乙未丙申之间。伤夷者未起。结卜未成头绪。而年谷大熟。常木一疋之价。多至租粟五六石。人不以出谷为难。故收合户口。以为粜籴。此乃事体当然。人亦不以为苦。何可以此比拟于今日之事乎。彼时则因时通变。以济大公。此事则移此困彼。未免有偏。揆以道理。实为未安。况今万口喁喁。举将颠壑。道殣相属。气象愁惨。假令孑遗馀民。不至尽灭。如大病之人。气息仅延。奄奄垂尽。正宜安其枕席。勿动勿摇。
自愿呈状于官前者。亦以其遑遑无告。至于无可奈何之域。故不暇顾他。有此无据之请。其势诚迫。而其情亦云戚矣。虽然事必正大。不乖于义理而无害于人。然后可行。今何可推己之所不欲。加之于无故之小户。但为利己之计而谓之可行乎。近于士人中有论此事者曰此法若行则于吾未收数多之人固为利矣。而揆之以事理则实有大不安于心。故不敢参入其中而赞成云。此言良是。还谷未收。积滞未纳者。所言如此。则其本无未收与下户之无田土。不得食还谷者之心。亦当何如也。此其不可行者一也。说者有以癸甲粜籴户口收合为證。以为可行。然其实有不同者。民尝闻故老之言矣。壬辰之祸惨矣。大盗满国。重以疠疫饥馑。民死殆尽。故 国家以保存遗民为念。凡系民间大小之役。一切倚阁。其于粜籴。尤所未遑。及其乙未丙申之间。伤夷者未起。结卜未成头绪。而年谷大熟。常木一疋之价。多至租粟五六石。人不以出谷为难。故收合户口。以为粜籴。此乃事体当然。人亦不以为苦。何可以此比拟于今日之事乎。彼时则因时通变。以济大公。此事则移此困彼。未免有偏。揆以道理。实为未安。况今万口喁喁。举将颠壑。道殣相属。气象愁惨。假令孑遗馀民。不至尽灭。如大病之人。气息仅延。奄奄垂尽。正宜安其枕席。勿动勿摇。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8H 页
 苟为不然。少或搅摇。则其死必速。此事之可见者也。八结户口。虽一样无异。而八结则犹是有田土之人也。至于贫人小户无田土者。则尤无所聊赖。诗所谓哿矣富人。哀此茕独。文王所以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皆此类也。虽使有所食还谷。犹当在分拣缓督之例。其忍以此横加于其身。使不得保存乎。此其不可行者二也。民闻大户所定十馀石。小户不下二石云。若然则其于以八结多食还谷之人。而纳户口还谷者。则固为大利。宜其乐之。而以八结之年年毕纳。无未收者。及贫残小户之无田土者言之。则死易而备纳难何者。民近听于农人之言。若还谷收捧之令一下。而户口人贸纳者遍于一境。则市价必益缩。以此推之则皮谷一石之价。应不下二十馀疋。而数内米豆之价。又为倍增。以春夏间卖尽竭乏之民。何处办出此许多价木。以应白地所不食之还谷乎。不惟此也。凶年谷主例为贵卖。掠削量给。故市上所贸之谷。欠缩居多。以之律之于还谷所纳之斗。则又加欠缩。必添数作石。及到仓所。又为库子所刀镫。辄以槩子钩取谷物于斛内一头。使民充其虚头。然后方引槩子而量之。至其耗数则又高重捧之。故欲纳一石则除非二十馀斗不可。而米豆耗数之价。又在其外。以此言之则小户二石之价。应不下五十馀疋。此岂无
苟为不然。少或搅摇。则其死必速。此事之可见者也。八结户口。虽一样无异。而八结则犹是有田土之人也。至于贫人小户无田土者。则尤无所聊赖。诗所谓哿矣富人。哀此茕独。文王所以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皆此类也。虽使有所食还谷。犹当在分拣缓督之例。其忍以此横加于其身。使不得保存乎。此其不可行者二也。民闻大户所定十馀石。小户不下二石云。若然则其于以八结多食还谷之人。而纳户口还谷者。则固为大利。宜其乐之。而以八结之年年毕纳。无未收者。及贫残小户之无田土者言之。则死易而备纳难何者。民近听于农人之言。若还谷收捧之令一下。而户口人贸纳者遍于一境。则市价必益缩。以此推之则皮谷一石之价。应不下二十馀疋。而数内米豆之价。又为倍增。以春夏间卖尽竭乏之民。何处办出此许多价木。以应白地所不食之还谷乎。不惟此也。凶年谷主例为贵卖。掠削量给。故市上所贸之谷。欠缩居多。以之律之于还谷所纳之斗。则又加欠缩。必添数作石。及到仓所。又为库子所刀镫。辄以槩子钩取谷物于斛内一头。使民充其虚头。然后方引槩子而量之。至其耗数则又高重捧之。故欲纳一石则除非二十馀斗不可。而米豆耗数之价。又在其外。以此言之则小户二石之价。应不下五十馀疋。此岂无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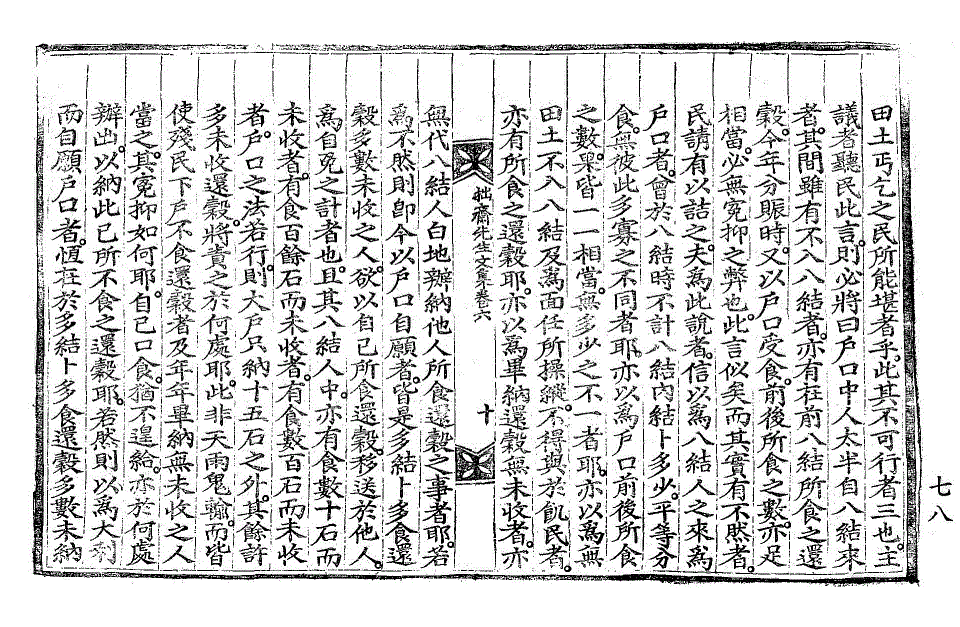 田土丐乞之民所能堪者乎。此其不可行者三也。主议者听民此言。则必将曰户口中人太半自八结来者。其间虽有不入八结者。亦有在前八结所食之还谷。今年分赈时。又以户口受食。前后所食之数。亦足相当。必无冤㧕之弊也。此言似矣而其实有不然者。民请有以诘之。夫为此说者。信以为八结人之来为户口者。曾于八结时不计八结内结卜多少。平等分食。无彼此多寡之不同者耶。亦以为户口前后所食之数。果皆一一相当。无多少之不一者耶。亦以为无田土不入八结及为面任所操纵。不得与于饥民者。亦有所食之还谷耶。亦以为毕纳还谷无未收者。亦无代八结人白地办纳他人所食还谷之事者耶。若为不然则即今以户口自愿者。皆是多结卜多食还谷多数未收之人。欲以自已所食还谷。移送于他人。为自免之计者也。且其八结人中。亦有食数十石而未收者。有食百馀石而未收者。有食数百石而未收者。户口之法若行。则大户只纳十五石之外。其馀许多未收还谷。将责之于何处耶。此非天雨鬼输。而皆使残民下户不食还谷者及年年毕纳无未收之人当之。其冤抑如何耶。自已口食。犹不遑给。亦于何处办出。以纳此已所不食之还谷耶。若然则以为大利而自愿户口者。恒在于多结卜多食还谷多数未纳
田土丐乞之民所能堪者乎。此其不可行者三也。主议者听民此言。则必将曰户口中人太半自八结来者。其间虽有不入八结者。亦有在前八结所食之还谷。今年分赈时。又以户口受食。前后所食之数。亦足相当。必无冤㧕之弊也。此言似矣而其实有不然者。民请有以诘之。夫为此说者。信以为八结人之来为户口者。曾于八结时不计八结内结卜多少。平等分食。无彼此多寡之不同者耶。亦以为户口前后所食之数。果皆一一相当。无多少之不一者耶。亦以为无田土不入八结及为面任所操纵。不得与于饥民者。亦有所食之还谷耶。亦以为毕纳还谷无未收者。亦无代八结人白地办纳他人所食还谷之事者耶。若为不然则即今以户口自愿者。皆是多结卜多食还谷多数未收之人。欲以自已所食还谷。移送于他人。为自免之计者也。且其八结人中。亦有食数十石而未收者。有食百馀石而未收者。有食数百石而未收者。户口之法若行。则大户只纳十五石之外。其馀许多未收还谷。将责之于何处耶。此非天雨鬼输。而皆使残民下户不食还谷者及年年毕纳无未收之人当之。其冤抑如何耶。自已口食。犹不遑给。亦于何处办出。以纳此已所不食之还谷耶。若然则以为大利而自愿户口者。恒在于多结卜多食还谷多数未纳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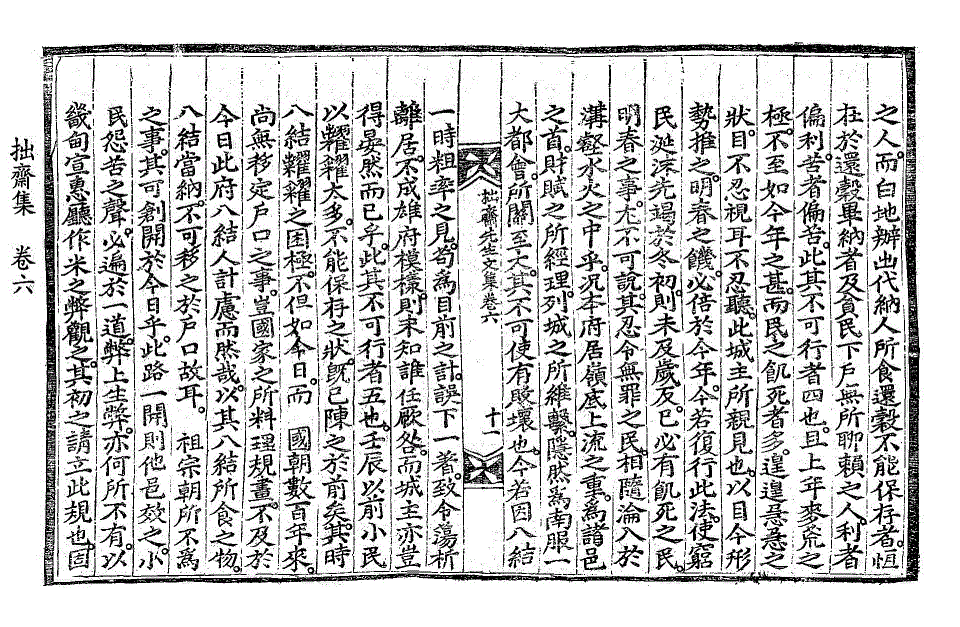 之人。而白地办出代纳人所食还谷不能保存者。恒在于还谷毕纳者及贫民。下户无所聊赖之人。利者偏利。苦者偏苦。此其不可行者四也。且上年麦荒之极。不至如今年之甚。而民之饥死者多。遑遑急急之状。目不忍视耳不忍听。此城主所亲见也。以目今形势推之。明春之饥。必倍于今年。今若复行此法。使穷民涎沫先竭于冬初。则未及岁反。已必有饥死之民。明春之事。尤不可说。其忍令无罪之民。相随沦入于沟壑水火之中乎。况本府居岭底上流之重。为诸邑之首。财赋之所经理。列城之所维系。隐然为南服一大都会。所关至大。其不可使有败坏也。今若因八结一时粗率之见。苟为目前之计。误下一著。致令荡析离居。不成雄府模样。则未知谁任厥咎。而城主亦岂得晏然而已乎。此其不可行者五也。壬辰以前小民以粜籴太多。不能保存之状。既已陈之于前矣。其时八结粜籴之困极。不但如今日。而 国朝数百年来。尚无移定户口之事。岂国家之所料理规画。不及于今日此府八结人计虑而然哉。以其八结所食之物。八结当纳。不可移之于户口故耳。 祖宗朝所不为之事。其可创开于今日乎。此路一开则他邑效之。小民怨苦之声。必遍于一道。弊上生弊。亦何所不有。以畿甸宣惠厅作米之弊观之。其初之请立此规也。固
之人。而白地办出代纳人所食还谷不能保存者。恒在于还谷毕纳者及贫民。下户无所聊赖之人。利者偏利。苦者偏苦。此其不可行者四也。且上年麦荒之极。不至如今年之甚。而民之饥死者多。遑遑急急之状。目不忍视耳不忍听。此城主所亲见也。以目今形势推之。明春之饥。必倍于今年。今若复行此法。使穷民涎沫先竭于冬初。则未及岁反。已必有饥死之民。明春之事。尤不可说。其忍令无罪之民。相随沦入于沟壑水火之中乎。况本府居岭底上流之重。为诸邑之首。财赋之所经理。列城之所维系。隐然为南服一大都会。所关至大。其不可使有败坏也。今若因八结一时粗率之见。苟为目前之计。误下一著。致令荡析离居。不成雄府模样。则未知谁任厥咎。而城主亦岂得晏然而已乎。此其不可行者五也。壬辰以前小民以粜籴太多。不能保存之状。既已陈之于前矣。其时八结粜籴之困极。不但如今日。而 国朝数百年来。尚无移定户口之事。岂国家之所料理规画。不及于今日此府八结人计虑而然哉。以其八结所食之物。八结当纳。不可移之于户口故耳。 祖宗朝所不为之事。其可创开于今日乎。此路一开则他邑效之。小民怨苦之声。必遍于一道。弊上生弊。亦何所不有。以畿甸宣惠厅作米之弊观之。其初之请立此规也。固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79L 页
 因畿甸民愿而为之。法非不美。而年久之后。其弊渐生。他役并兴。故宣惠厅所纳之米。反为别件叠役。此亦城主之所亲闻也。以宣惠厅便民之法。尚且如此。况此病民不平之甚。已见于始议之初。末流之弊。何可防乎。此其不可行者六也。大凡事出于正而无害于义理。则不计利害而为之可也。今此事则害于义者不一而足。前有八结利己之嫌。后有残户难保之害。已非中正可行之道。而其为后弊。不可胜言。又何可行乎。伏愿城主更加详察而善处焉。
因畿甸民愿而为之。法非不美。而年久之后。其弊渐生。他役并兴。故宣惠厅所纳之米。反为别件叠役。此亦城主之所亲闻也。以宣惠厅便民之法。尚且如此。况此病民不平之甚。已见于始议之初。末流之弊。何可防乎。此其不可行者六也。大凡事出于正而无害于义理。则不计利害而为之可也。今此事则害于义者不一而足。前有八结利己之嫌。后有残户难保之害。已非中正可行之道。而其为后弊。不可胜言。又何可行乎。伏愿城主更加详察而善处焉。与金光庭(煃)别纸(庚戌)
近闻或以上洛公为武烈有歉焉之议。不胜慨然之至。夫以公当胡元窃据之际。所谓洪茶丘达鲁花赤之徒。肆其凶虐。横起大狱。欲以构陷丽主。拷掠公备极惨毒。丽主使之诬服。而公抗辞不挠。竟白其诬。使其君得脱于难而宗社再安。其忠盛矣。而扬名显亲。孝亦克尽。千古纲常。赖而不坠。其有功于名教甚大。孟子所谓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者非耶。夫士之馀力学文。讨论古训。正欲讲明此理。体之于身。见之于行耳。故子夏曰吾必谓之已学。而朱夫子亦曰学求如是而已。公之所树立。既如彼卓卓。辉映宇宙。耸动方来。则其可以武烈而少之哉。况鹤沙于玆院创始之初。表而出之。昭揭院号。其意所在。实非偶然。则云云之说。尤不当作于其间。如何如何。且有一事。鹤沙之于上洛。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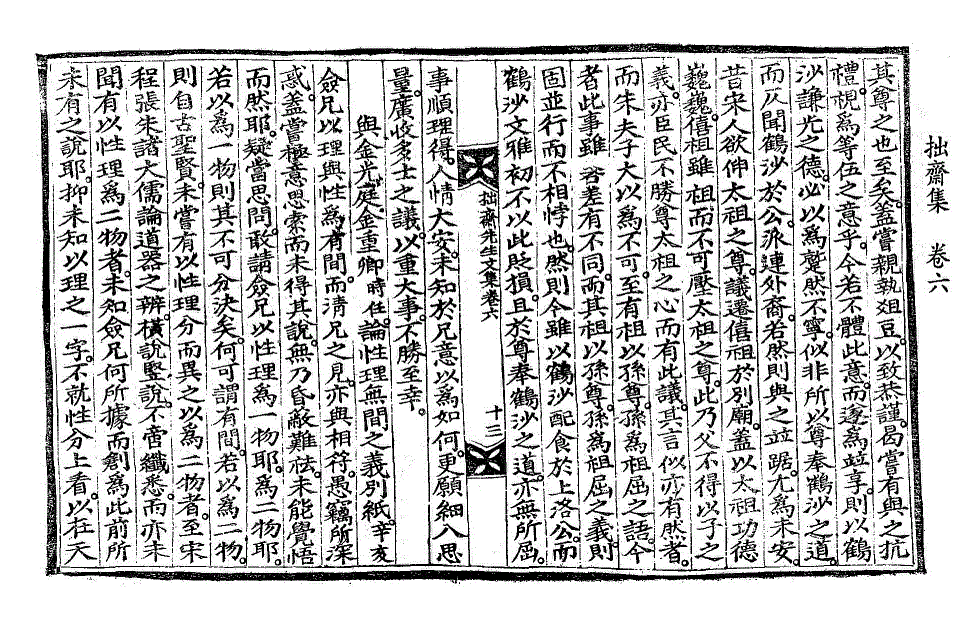 其尊之也至矣。盖尝亲执俎豆。以致恭谨。曷尝有与之抗礼。视为等伍之意乎。今若不体此意。而遂为并享。则以鹤沙谦光之德。必以为蹴然不宁。似非所以尊奉鹤沙之道。而仄闻鹤沙于公。派连外裔。若然则与之并踞。尤为未安。昔宋人欲伸太祖之尊。议迁僖祖于别庙。盖以太祖功德巍巍。僖祖虽祖而不可压太祖之尊。此乃父不得以子之义。亦臣民不胜尊太祖之心而有此议。其言似亦有然者。而朱夫子大以为不可。至有祖以孙尊。孙为祖屈之语。今者此事虽若差有不同。而其祖以孙尊。孙为祖屈之义。则固并行而不相悖也。然则今虽以鹤沙配食于上洛公。而鹤沙文雅初不以此贬损。且于尊奉鹤沙之道。亦无所屈。事顺理得。人情大安。未知于兄意以为如何。更愿细入思量。广收多士之议。以重大事。不胜至幸。
其尊之也至矣。盖尝亲执俎豆。以致恭谨。曷尝有与之抗礼。视为等伍之意乎。今若不体此意。而遂为并享。则以鹤沙谦光之德。必以为蹴然不宁。似非所以尊奉鹤沙之道。而仄闻鹤沙于公。派连外裔。若然则与之并踞。尤为未安。昔宋人欲伸太祖之尊。议迁僖祖于别庙。盖以太祖功德巍巍。僖祖虽祖而不可压太祖之尊。此乃父不得以子之义。亦臣民不胜尊太祖之心而有此议。其言似亦有然者。而朱夫子大以为不可。至有祖以孙尊。孙为祖屈之语。今者此事虽若差有不同。而其祖以孙尊。孙为祖屈之义。则固并行而不相悖也。然则今虽以鹤沙配食于上洛公。而鹤沙文雅初不以此贬损。且于尊奉鹤沙之道。亦无所屈。事顺理得。人情大安。未知于兄意以为如何。更愿细入思量。广收多士之议。以重大事。不胜至幸。与金光庭,金重卿(时任)。论性理无间之义别纸。(辛亥)
佥兄以理与性为有间。而清兄之见。亦与相符。愚窃所深惑。盖尝极意思索而未得其说。无乃昏蔽难祛。未能觉悟而然耶。疑当思问。敢请佥兄以性理为一物耶。为二物耶。若以为一物则其不可分决矣。何可谓有间。若以为二物。则自古圣贤。未尝有以性理分而异之以为二物者。至宋程张朱诸大儒论道器之辨。横说竖说。不啻纤悉。而亦未闻有以性理为二物者。未知佥兄何所据而创为此前所未有之说耶。抑未知以理之一字。不就性分上看。以在天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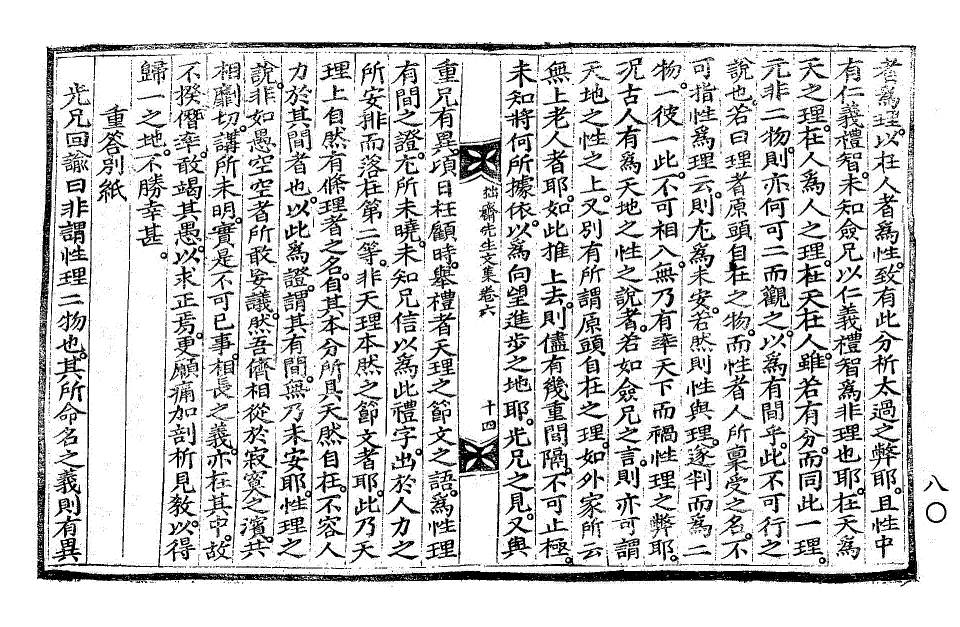 者为理。以在人者为性。致有此分析太过之弊耶。且性中有仁义礼智。未知佥兄以仁义礼智为非理也耶。在天为天之理。在人为人之理。在天在人。虽若有分。而同此一理。元非二物。则亦何可二而观之。以为有间乎。此不可行之说也。若曰理者原头自在之物。而性者人所禀受之名。不可指性为理云。则尤为未安。若然则性与理。遂判而为二物。一彼一此。不可相入。无乃有率天下而祸性理之弊耶。况古人有为天地之性之说者。若如佥兄之言。则亦可谓天地之性之上。又别有所谓原头自在之理。如外家所云无上老人者耶。如此推上去。则尽有几重间隔。不可止极。未知将何所据依。以为向望进步之地耶。先兄之见。又与重兄有异。顷日枉顾时。举礼者天理之节文之语。为性理有间之證。尤所未晓。未知兄信以为此礼字。出于人力之所安排而落在第二等。非天理本然之节文者耶。此乃天理上自然有条理者之名。自其本分所具天然自在。不容人力于其间者也。以此为證。谓其有间。无乃未安耶。性理之说。非如愚空空者所敢妄议。然吾侪相从于寂寞之滨。共相劘切。讲所未明。实是不可已事。相长之义。亦在其中。故不揆僭率。敢竭其愚。以求正焉。更愿痛加剖析见教。以得归一之地。不胜幸甚。
者为理。以在人者为性。致有此分析太过之弊耶。且性中有仁义礼智。未知佥兄以仁义礼智为非理也耶。在天为天之理。在人为人之理。在天在人。虽若有分。而同此一理。元非二物。则亦何可二而观之。以为有间乎。此不可行之说也。若曰理者原头自在之物。而性者人所禀受之名。不可指性为理云。则尤为未安。若然则性与理。遂判而为二物。一彼一此。不可相入。无乃有率天下而祸性理之弊耶。况古人有为天地之性之说者。若如佥兄之言。则亦可谓天地之性之上。又别有所谓原头自在之理。如外家所云无上老人者耶。如此推上去。则尽有几重间隔。不可止极。未知将何所据依。以为向望进步之地耶。先兄之见。又与重兄有异。顷日枉顾时。举礼者天理之节文之语。为性理有间之證。尤所未晓。未知兄信以为此礼字。出于人力之所安排而落在第二等。非天理本然之节文者耶。此乃天理上自然有条理者之名。自其本分所具天然自在。不容人力于其间者也。以此为證。谓其有间。无乃未安耶。性理之说。非如愚空空者所敢妄议。然吾侪相从于寂寞之滨。共相劘切。讲所未明。实是不可已事。相长之义。亦在其中。故不揆僭率。敢竭其愚。以求正焉。更愿痛加剖析见教。以得归一之地。不胜幸甚。与金光庭,金重卿。论性理无间之义别纸。[重答别纸]
光兄回谕曰非谓性理二物也。其所命名之义则有异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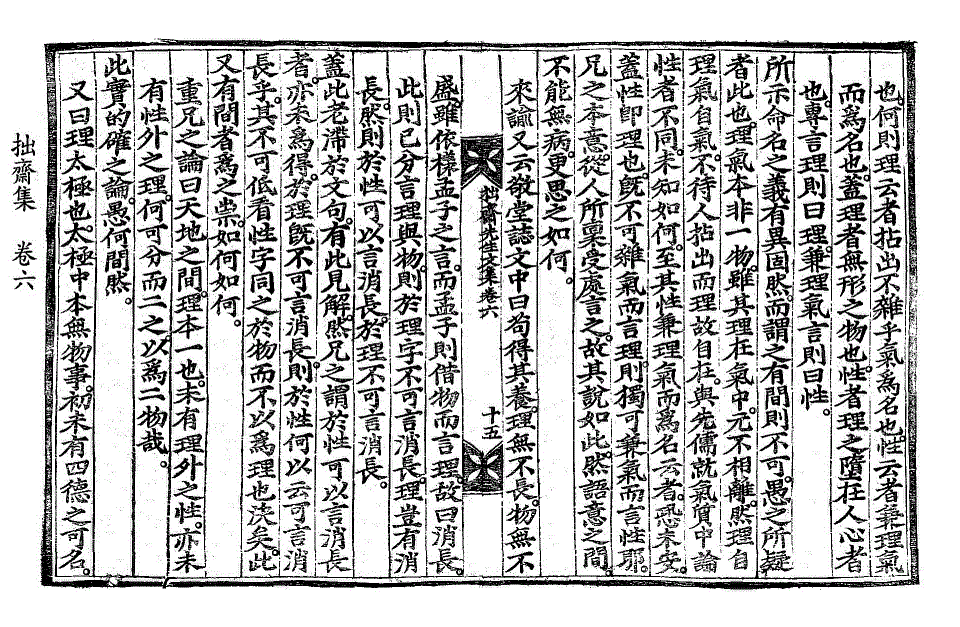 也。何则理云者拈出不杂乎气为名也。性云者兼理气而为名也。盖理者无形之物也。性者理之堕在人心者也。专言理则曰理。兼理气言则曰性。
也。何则理云者拈出不杂乎气为名也。性云者兼理气而为名也。盖理者无形之物也。性者理之堕在人心者也。专言理则曰理。兼理气言则曰性。所示命名之义有异固然。而谓之有间则不可。愚之所疑者此也。理气本非一物。虽其理在气中。元不相离。然理自理气自气。不待人拈出而理故自在。与先儒就气质中论性者不同。未知如何。至其性兼理气而为名云者。恐未安。盖性即理也。既不可杂气而言理。则独可兼气而言性耶。兄之本意。从人所禀受处言之。故其说如此。然语意之间。不能无病。更思之如何。
来谕又云敬堂志文中曰苟得其养。理无不长。物无不盛。虽依样孟子之言。而孟子则借物而言理。故曰消长。此则已分言理与物。则于理字不可言消长。理岂有消长。然则于性可以言消长。于理不可言消长。
盖此老滞于文句。有此见解。然兄之谓于性可以言消长者。亦未为得。于理既不可言消长。则于性何以云可言消长乎。其不可低看性字同之于物而不以为理也决矣。此又有间者为之祟。如何如何。
重兄之论曰天地之间。理本一也。未有理外之性。亦未有性外之理。何可分而二之。以为二物哉。
此实的确之论。愚何间然。
又曰理太极也。太极中本无物事。初未有四德之可名。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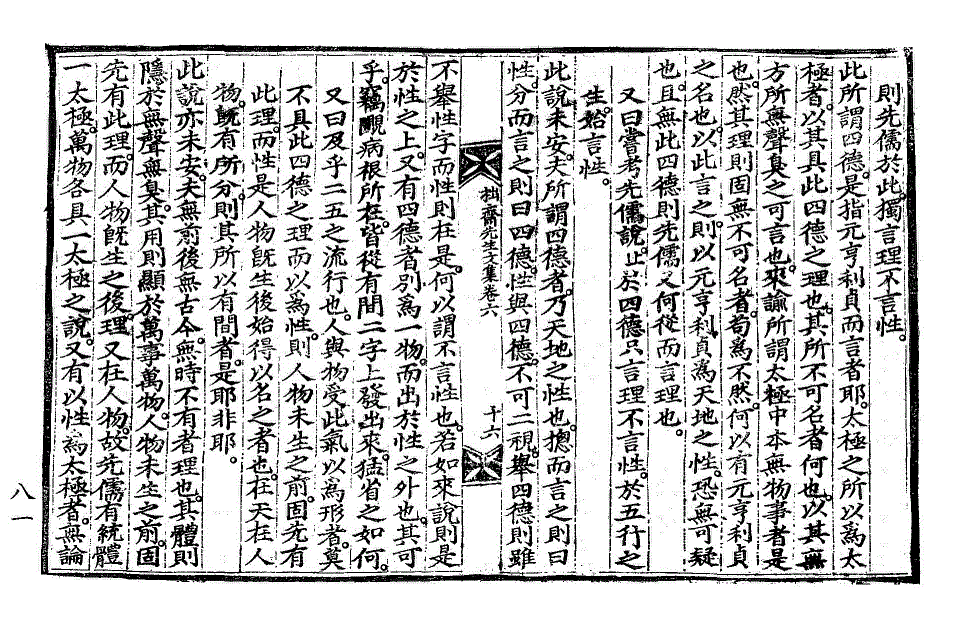 则先儒于此。独言理不言性。
则先儒于此。独言理不言性。此所谓四德。是指元亨利贞而言者耶。太极之所以为太极者。以其具此四德之理也。其所不可名者何也。以其无方所无声臭之可言也。来谕所谓太极中本无物事者是也。然其理则固无不可名者。苟为不然。何以有元亨利贞之名也。以此言之。则以元亨利贞为天地之性。恐无可疑也。且无此四德则先儒又何从而言理也。
又曰尝考先儒说。(止)于四德只言理不言性。于五行之生。始言性。
此说未安。夫所谓四德者。乃天地之性也。总而言之则曰性。分而言之则曰四德。性与四德。不可二视。举四德则虽不举性字而性则在是。何以谓不言性也。若如来说则是于性之上。又有四德者别为一物。而出于性之外也。其可乎。窃覸病根所在。皆从有间二字上发出来。猛省之如何。
又曰及乎二五之流行也。人与物受此气以为形者。莫不具此四德之理而以为性。则人物未生之前。固先有此理。而性是人物既生后始得以名之者也。在天在人物。既有所分。则其所以有间者。是耶非耶。
此说亦未安。夫无前后无古今。无时不有者理也。其体则隐于无声无臭。其用则显于万事万物。人物未生之前。固先有此理。而人物既生之后。理又在人物。故先儒有统体一太极。万物各具一太极之说。又有以性为太极者。无论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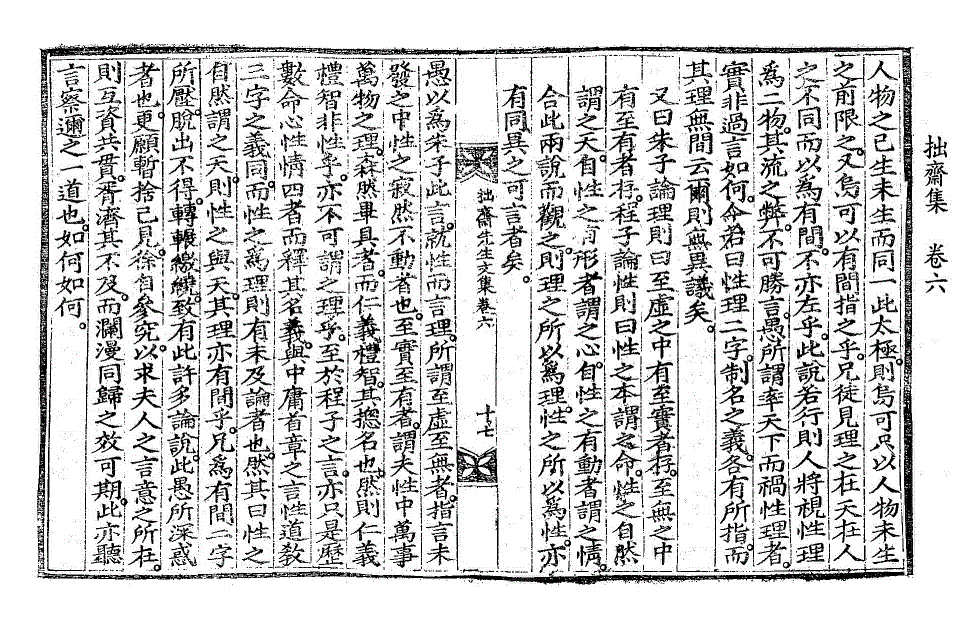 人物之已生未生而同一此太极。则乌可只以人物未生之前限之。又乌可以有间指之乎。兄徒见理之在天在人之不同而以为有间。不亦左乎。此说若行则人将视性理为二物。其流之弊。不可胜言。愚所谓率天下而祸性理者。实非过言如何。今若曰性理二字。制名之义。各有所指。而其理无间云尔则无异议矣。
人物之已生未生而同一此太极。则乌可只以人物未生之前限之。又乌可以有间指之乎。兄徒见理之在天在人之不同而以为有间。不亦左乎。此说若行则人将视性理为二物。其流之弊。不可胜言。愚所谓率天下而祸性理者。实非过言如何。今若曰性理二字。制名之义。各有所指。而其理无间云尔则无异议矣。又曰朱子论理则曰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至无之中有至有者存。程子论性则曰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合此两说而观之。则理之所以为理。性之所以为性。亦有同异之可言者矣。
愚以为朱子此言。就性而言理。所谓至虚至无者。指言未发之中性之寂然不动者也。至实至有者。谓夫性中万事万物之理。森然毕具者。而仁义礼智。其总名也。然则仁义礼智非性乎。亦不可谓之理乎。至于程子之言。亦只是历数命心性情四者而释其名义。与中庸首章之言性道教三字之义同。而性之为理则有未及论者也。然其曰性之自然谓之天。则性之与天。其理亦有间乎。兄为有间二字所压。脱出不得。转辗缴绕。致有此许多论说。此愚所深惑者也。更愿暂舍己见。徐自参究。以求夫人之言意之所在。则互资共贯。胥济其不及。而澜漫同归之效可期。此亦听言察迩之一道也。如何如何。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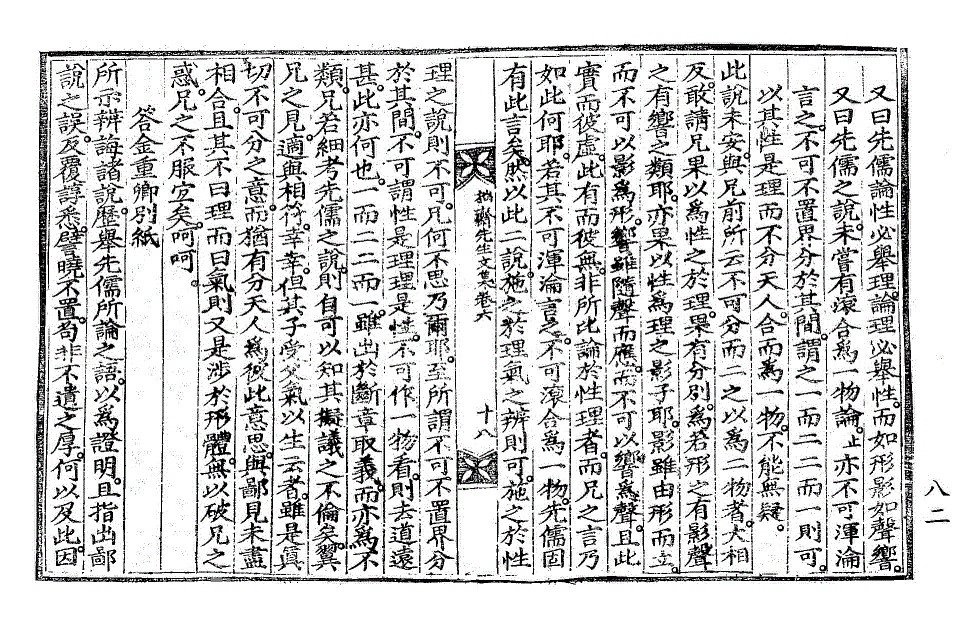 又曰先儒论性必举理。论理必举性。而如形影如声响。又曰先儒之说。未尝有滚合为一物论。(止)亦不可浑沦言之。不可不置界分于其间。谓之一而二二而一则可。以其性是理而不分天人。合而为一物。不能无疑。
又曰先儒论性必举理。论理必举性。而如形影如声响。又曰先儒之说。未尝有滚合为一物论。(止)亦不可浑沦言之。不可不置界分于其间。谓之一而二二而一则可。以其性是理而不分天人。合而为一物。不能无疑。此说未安。与兄前所云不可分而二之以为二物者。大相反。敢请兄果以为性之于理。果有分别。为若形之有影声之有响之类耶。亦果以性为理之影子耶。影虽由形而立。而不可以影为形。响虽随声而应。而不可以响为声。且此实而彼虚。此有而彼无。非所比论于性理者。而兄之言乃如此何耶。若其不可浑沦言之。不可滚合为一物。先儒固有此言矣。然以此二说。施之于理气之辨则可。施之于性理之说则不可。兄何不思乃尔耶。至所谓不可不置界分于其间。不可谓性是理理是性。不可作一物看。则去道远甚。此亦何也。一而二二而一。虽出于断章取义。而亦为不类。兄若细考先儒之说。则自可以知其拟议之不伦矣。翼兄之见。适与相符。幸幸。但其子受父气以生云者。虽是真切不可分之意。而犹有分天人为彼此意思。与鄙见未尽相合。且其不曰理而曰气则又是涉于形体。无以破兄之惑。兄之不服宜矣。呵呵。
答金重卿别纸
所示辨诲诸说。历举先儒所论之语。以为證明。且指出鄙说之误。反覆谆悉。譬晓不置。苟非不遗之厚。何以及此。因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3H 页
 以益闻所未闻。亦自觉其未及称停之失。为赐多矣。但于其间亦有未能契悟者。故敢复一二以求正。幸愿痛赐镌诲。
以益闻所未闻。亦自觉其未及称停之失。为赐多矣。但于其间亦有未能契悟者。故敢复一二以求正。幸愿痛赐镌诲。辨诲曰来谕就本然上说内。兄就气质上说。宜乎两言之不相入也。又曰先儒有合虚与气而性全之语。其言兼理气者。亦不为病。
元来鄙说是直论性之体段。与就气质中拈出而论性者。其意自不同也。故愚于前书。以为不可兼气而言性。诚以性虽在气质之中。而不以气质之不齐而有所消长故耳。盖尊而无对者理也。为物之主而不命于物者亦理也。今若以先儒合虚与气之说而兼气质言之。则无乃看不得本来面目耶。
辨诲举先生天命图说中论元亨利贞之语而结之曰其未始流行之前。元亨利贞之理。果何从而名之乎。
愚以为先生此言。就天之赋于物者言之。故有此言。然其始而通通而遂遂而成者。毕竟先有此理。故有此始通遂成之流行。若非先有此理。则所谓始通遂成者。从何而出乎。以此推之则先生所谓太极中本无物事。初岂有四德之可名者。以其未发也。冲漠无眹不可见。而及其流行之后始可见。故言之耳。岂真以为元无此理。乃于流行之后始有此理。而有所云云乎。夫人之性。亦一太极也。方其未发也。真一之理。湛然在中。固亦无声臭无形体之可名。而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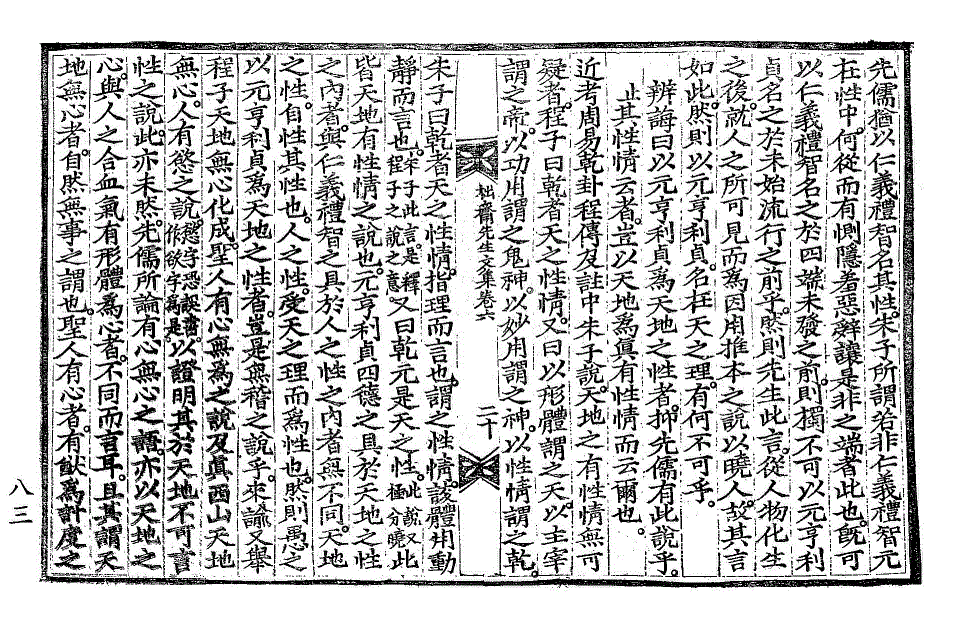 先儒犹以仁义礼智名其性。朱子所谓若非仁义礼智元在性中。何从而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者此也。既可以仁义礼智名之于四端未发之前。则独不可以元亨利贞名之于未始流行之前乎。然则先生此言。从人物化生之后。就人之所可见而为因用推本之说以晓人。故其言如此。然则以元亨利贞。名在天之理。有何不可乎。
先儒犹以仁义礼智名其性。朱子所谓若非仁义礼智元在性中。何从而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者此也。既可以仁义礼智名之于四端未发之前。则独不可以元亨利贞名之于未始流行之前乎。然则先生此言。从人物化生之后。就人之所可见而为因用推本之说以晓人。故其言如此。然则以元亨利贞。名在天之理。有何不可乎。辨诲曰以元亨利贞为天地之性者。抑先儒有此说乎。(止)其性情云者。岂以天地为真有性情而云尔也。
近考周易乾卦程传及注中朱子说。天地之有性情无可疑者。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又曰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朱子曰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谓之性情。该体用动静而言也。(朱子此言。是释程子之说之意。)又曰乾元是天之性。(此说又极分晓)此皆天地有性情之说也。元亨利贞四德之具于天地之性之内者。与仁义礼智之具于人之性之内者无不同。天地之性。自性其性也。人之性。受天之理而为性也。然则愚之以元亨利贞为天地之性者。岂是无稽之说乎。来谕又举程子天地无心化成。圣人有心无为之说及真西山天地无心。人有欲之说。(欲字恐误书。作欲字为是。)以證明其于天地不可言性之说。此亦未然。先儒所论有心无心之语。亦以天地之心。与人之合血气有形体为心者。不同而言耳。且其谓天地无心者。自然无事之谓也。圣人有心者。有猷为计度之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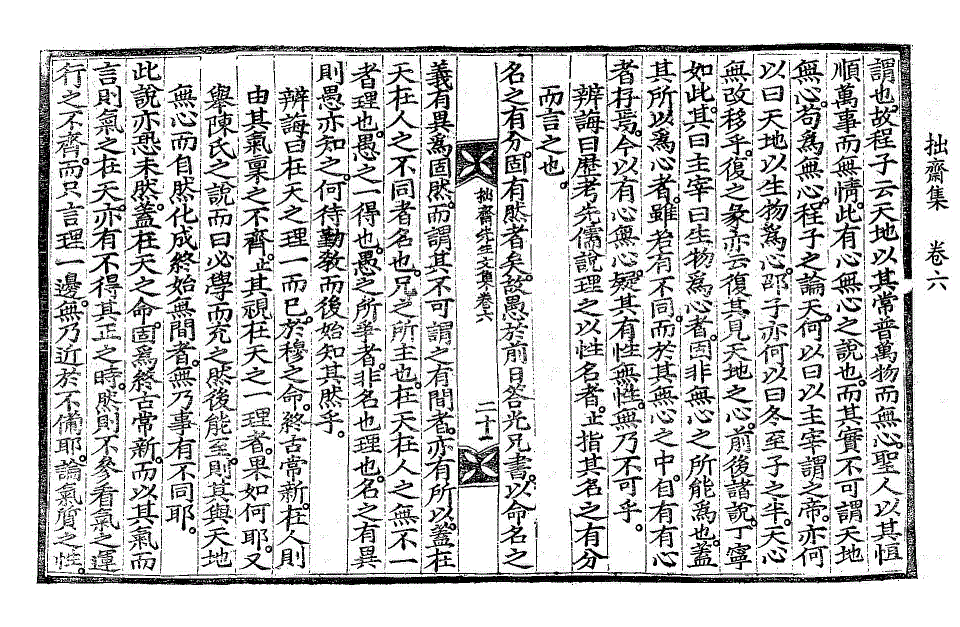 谓也。故程子云天地以其常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以其恒顺万事而无情。此有心无心之说也。而其实不可谓天地无心。苟为无心。程子之论天。何以曰以主宰谓之帝。亦何以曰天地以生物为心。邵子亦何以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乎。复之彖亦云复其见天地之心。前后诸说。丁宁如此。其曰主宰曰生物为心者。固非无心之所能为也。盖其所以为心者。虽若有不同。而于其无心之中。自有有心者存焉。今以有心无心。疑其有性无性。无乃不可乎。
谓也。故程子云天地以其常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以其恒顺万事而无情。此有心无心之说也。而其实不可谓天地无心。苟为无心。程子之论天。何以曰以主宰谓之帝。亦何以曰天地以生物为心。邵子亦何以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乎。复之彖亦云复其见天地之心。前后诸说。丁宁如此。其曰主宰曰生物为心者。固非无心之所能为也。盖其所以为心者。虽若有不同。而于其无心之中。自有有心者存焉。今以有心无心。疑其有性无性。无乃不可乎。辨诲曰历考先儒说理之以性名者。(止)指其名之有分而言之也。
名之有分。固有然者矣。故愚于前日答光兄书。以命名之义有异为固然。而谓其不可谓之有间者。亦有所以。盖在天在人之不同者名也。兄之所主也。在天在人之无不一者理也。愚之一得也。愚之所争者。非名也理也。名之有异则愚亦知之。何待勤教而后始知其然乎。
辨诲曰在天之理一而已。于穆之命。终古常新。在人则由其气禀之不齐。(止)其视在天之一理者。果如何耶。又举陈氏之说而曰必学而充之然后能至。则其与天地无心而自然化成终始无间者。无乃事有不同耶。
此说亦恐未然。盖在天之命。固为终古常新。而以其气而言则气之在天。亦有不得其正之时。然则不参看气之运行之不齐。而只言理一边。无乃近于不备耶。论气质之性。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4L 页
 亦当通圣愚而言。而今但就众人气质上言。而不言圣人气质清粹。与天为一之性。无乃近于不明耶ㅊ况今之所论者性也。惟当论性之体段。而言其与天无间之妙可也。何必兼气言性。以为天之与人。事有同异乎。
亦当通圣愚而言。而今但就众人气质上言。而不言圣人气质清粹。与天为一之性。无乃近于不明耶ㅊ况今之所论者性也。惟当论性之体段。而言其与天无间之妙可也。何必兼气言性。以为天之与人。事有同异乎。辨诲曰形影声响之谕。愚意实未知其为非也。又曰程子尝论义理。亦用此四字云云。又曰一而二二而一。虽未知其衬贴与否。而朱子尝论太极阴阳及心与性而亦用此四字。又曰性理也心亦理也。而朱子之言如此。则今论天理人性之理同义一。名异事异。而谓之一而二二而一。亦何病焉。
形影声响之说。虽闻有程子之训。而未能契悟可叹。愿从兄所得见程子所论本末。反覆详玩。则庶或有启发之端耶。(恐程子此言。自有所指而发。必不以形影声响。指性理而言。)至其朱子所论则此正理气之说也。理气自是二物。亦不相离。朱子之谓其一而二二而一。不亦宜乎。所示心亦理三字大误。若果心亦理。则朱子何以曰心犹阴阳也。盖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性者理也。心者盛贮理之器也。知不可以心为性。则可以知以心为理之不然矣。盖心具是理。举心而言则理在其中。故先儒或有为如此说者。如孟子之云仁人心是也。然若论心性之分。则心自是器。性自是理。其不可指心为理也。以大学明德注朱子所论之说看之。则心性之别。自可了然。如何如何。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5H 页
 辨诲又举程子以玉譬理之说而曰。假令有两玉。一大一小。大而为大器。小而为小器。以形体言之则虽有大小。论其理则同。语其德则一也。然形既有异。用各不同。则谓之一乎。谓之二乎。此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
辨诲又举程子以玉譬理之说而曰。假令有两玉。一大一小。大而为大器。小而为小器。以形体言之则虽有大小。论其理则同。语其德则一也。然形既有异。用各不同。则谓之一乎。谓之二乎。此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器之形体虽殊。而其为玉则一也。既曰理一则何以谓一而二二而一也。以此所示之说言之。亦可见性之为理。无有间隔矣。何不一意打开。无有芥滞。四通八达。玲珑自在。以玩夫快活气象。而必为此多少闲枝叶。令性中有夹杂有遮瞙。以汨其本来面目耶。一此不已则亦令心地缴绕。无和平𥳑易时节。为害不少。更思之如何。
与金光庭,金重卿书。(壬子)
近阅旧箧。得前年所与往复性理鄙说。其大意则然。而所以剖析者有未尽。玆敢更申前说。以竭其底蕴焉。幸望有以商量而细教之。盖性即理。而其所以有制名之异者何也。理者以物之有条理而为名也。天下之物。条理之密。莫如玉。而玉以土为田地。故理之为字。从玉从田从土。其义重在玉字上。性者以心具是理而为名也。理为心之主。而心者所以盛贮是理者也。理非心。理无挂搭处。故性之为字。从心从生。生者心中之生理。其义重在生字上。此其所以有制名之异也。然性自是理。虽令善言性者详辨而索言之。亦放下此理字不得。苟其放下此理字而言性。则性为无实不可形状之一虚名。而理亦离了性则亦无可摸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5L 页
 索指拟处。不成为理矣。盖性者理之原头统会底。故子思既以性为天下之大本。孟子亦谓万物皆备于我。其谓万物者。是指万物之理而言。而其谓皆备于我者。是指此理之悉具于性分之内而言也。然则性之得名以此理也。此乃朱子所谓性之骨子也。若果离了理则性之名义。索然尽矣。更将甚物而言性耶。心之所以为心者。亦以贮此理在中也。若离了理而失其所谓性。则是死个心也。若果如此则理不得为理。性不得为性。心亦不得为心。不足为万物之灵。亦不能为天下之大本矣。儒者之谈性理以明圣人之道者。恐不当若是。故前呈重兄书中。谓其但知二五。而不知十为目论者。实以此言也。夫目之明。能察秋毫之细而不能见其睫者非其明之有所不足。以其蔽于近而然也。所见一变于前。所守遂易于内。此非其所蔽使之然乎。今之言性而不以理看性。乃至于分而二之者。与此何以异也。兄之谓性有消长者。是以气看性之说也。重兄之主众人分上而论性。谓人与天不同者。亦以气看性之说也。但兄旋觉其误。而重兄一向坚执为可惜耳。若此以气看性之说。不得共为辨覈。而遂为口实于世。则其弊必至于使昧者见之。转辗迷误。卑者入于告子之以食色为性。大违于孟子君子有不性者焉之旨。高者流于释氏之以作用为性。猖狂自恣。不可如何。甚者陷于荀子性恶之见。以尧舜为伪。桀纣为性。其为害又将何以救之哉。尹和靖
索指拟处。不成为理矣。盖性者理之原头统会底。故子思既以性为天下之大本。孟子亦谓万物皆备于我。其谓万物者。是指万物之理而言。而其谓皆备于我者。是指此理之悉具于性分之内而言也。然则性之得名以此理也。此乃朱子所谓性之骨子也。若果离了理则性之名义。索然尽矣。更将甚物而言性耶。心之所以为心者。亦以贮此理在中也。若离了理而失其所谓性。则是死个心也。若果如此则理不得为理。性不得为性。心亦不得为心。不足为万物之灵。亦不能为天下之大本矣。儒者之谈性理以明圣人之道者。恐不当若是。故前呈重兄书中。谓其但知二五。而不知十为目论者。实以此言也。夫目之明。能察秋毫之细而不能见其睫者非其明之有所不足。以其蔽于近而然也。所见一变于前。所守遂易于内。此非其所蔽使之然乎。今之言性而不以理看性。乃至于分而二之者。与此何以异也。兄之谓性有消长者。是以气看性之说也。重兄之主众人分上而论性。谓人与天不同者。亦以气看性之说也。但兄旋觉其误。而重兄一向坚执为可惜耳。若此以气看性之说。不得共为辨覈。而遂为口实于世。则其弊必至于使昧者见之。转辗迷误。卑者入于告子之以食色为性。大违于孟子君子有不性者焉之旨。高者流于释氏之以作用为性。猖狂自恣。不可如何。甚者陷于荀子性恶之见。以尧舜为伪。桀纣为性。其为害又将何以救之哉。尹和靖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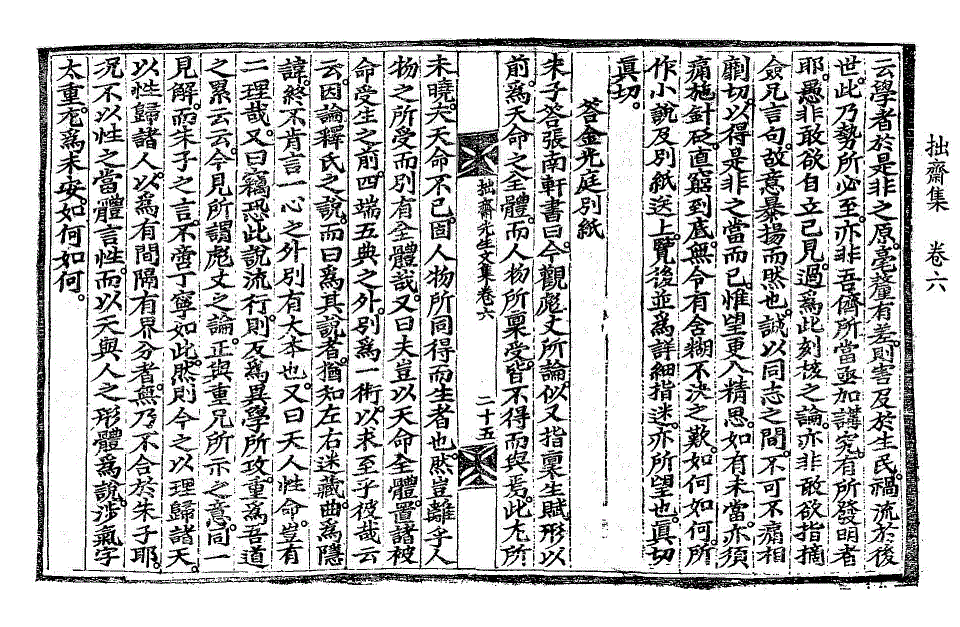 云学者于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则害及于生民。祸流于后世。此乃势所必至。亦非吾侪所当亟加讲究。有所发明者耶。愚非敢欲自立己见。过为此刻核之论。亦非敢欲指摘佥兄言句。故意暴扬而然也。诚以同志之间。不可不痛相劘切。以得是非之当而已。惟望更入精思。如有未当。亦须痛施针砭。直穷到底。无令有含糊不决之叹。如何如何。所作小说及别纸送上。览后并为详细指迷。亦所望也。真切真切。
云学者于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则害及于生民。祸流于后世。此乃势所必至。亦非吾侪所当亟加讲究。有所发明者耶。愚非敢欲自立己见。过为此刻核之论。亦非敢欲指摘佥兄言句。故意暴扬而然也。诚以同志之间。不可不痛相劘切。以得是非之当而已。惟望更入精思。如有未当。亦须痛施针砭。直穷到底。无令有含糊不决之叹。如何如何。所作小说及别纸送上。览后并为详细指迷。亦所望也。真切真切。答金光庭别纸
朱子答张南轩书曰。今观彪丈所论。似又指禀生赋形以前。为天命之全体。而人物所禀受。皆不得而与焉。此尤所未晓。夫天命不已。固人物所同得而生者也。然岂离乎人物之所受而别有全体哉。又曰夫岂以天命全体。置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别为一术。以求至乎彼哉云云。因论释氏之说。而曰为其说者。犹知左右迷藏。曲为隐讳。终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又曰天人性命。岂有二理哉。又曰窃恐此说流行。则反为异学所攻。重为吾道之累云云。今见所谓彪丈之论。正与重兄所示之意。同一见解。而朱子之言。不啻丁宁如此。然则今之以理归诸天。以性归诸人。以为有间隔有界分者。无乃不合于朱子耶。况不以性之当体言性。而以天与人之形体为说。涉气字太重。尤为未安。如何如何。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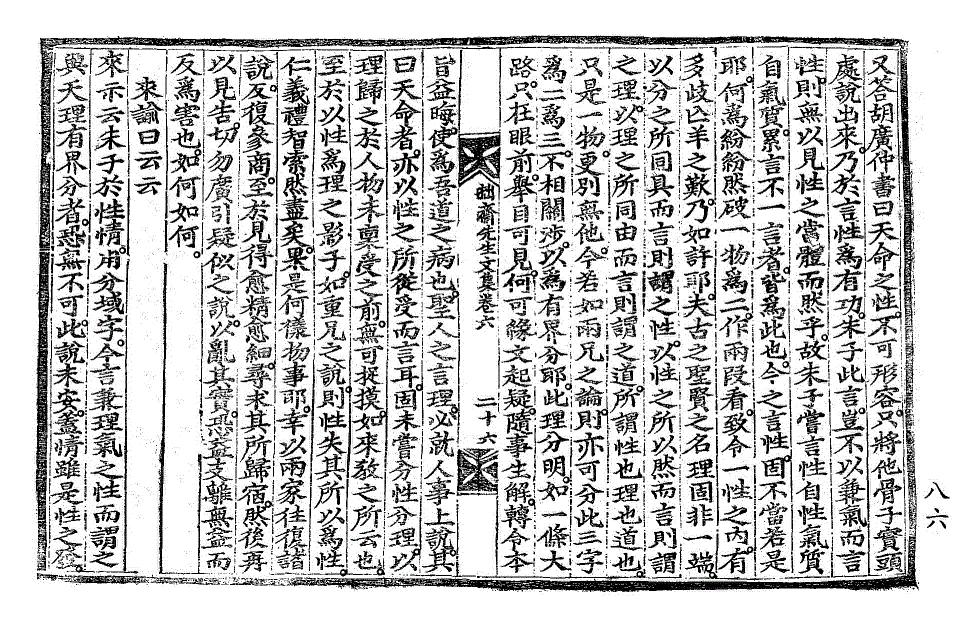 又答胡广仲书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只将他骨子实头处说出来。乃于言性为有功。朱子此言。岂不以兼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当体而然乎。故朱子尝言性自性气质自气质。累言不一言者。皆为此也。今之言性。固不当若是耶。何为纷纷然破一物为二。作两段看。致令一性之内。有多歧亡羊之叹。乃如许耶。夫古之圣贤之名理固非一端。以分之所同具而言则谓之性。以性之所以然而言则谓之理。以理之所同由而言则谓之道。所谓性也理也道也。只是一物。更别无他。今若如两兄之论。则亦可分此三字为二为三。不相关涉。以为有界分耶。此理分明。如一条大路。只在眼前。举目可见。何可缘文起疑。随事生解。转令本旨益晦。使为吾道之病也。圣人之言理。必就人事上说。其曰天命者。亦以性之所从受而言耳。固未尝分性分理。以理归之于人物未禀受之前。无可捉摸。如来教之所云也。至于以性为理之影子。如重兄之说。则性失其所以为性。仁义礼智索然尽矣。果是何样物事耶。幸以两家往复诸说。反复参商。至于见得愈精愈细。寻求其所归宿。然后再以见告。切勿广引疑似之说。以乱其实。恐益支离无益而反为害也。如何如何。
又答胡广仲书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只将他骨子实头处说出来。乃于言性为有功。朱子此言。岂不以兼气而言性。则无以见性之当体而然乎。故朱子尝言性自性气质自气质。累言不一言者。皆为此也。今之言性。固不当若是耶。何为纷纷然破一物为二。作两段看。致令一性之内。有多歧亡羊之叹。乃如许耶。夫古之圣贤之名理固非一端。以分之所同具而言则谓之性。以性之所以然而言则谓之理。以理之所同由而言则谓之道。所谓性也理也道也。只是一物。更别无他。今若如两兄之论。则亦可分此三字为二为三。不相关涉。以为有界分耶。此理分明。如一条大路。只在眼前。举目可见。何可缘文起疑。随事生解。转令本旨益晦。使为吾道之病也。圣人之言理。必就人事上说。其曰天命者。亦以性之所从受而言耳。固未尝分性分理。以理归之于人物未禀受之前。无可捉摸。如来教之所云也。至于以性为理之影子。如重兄之说。则性失其所以为性。仁义礼智索然尽矣。果是何样物事耶。幸以两家往复诸说。反复参商。至于见得愈精愈细。寻求其所归宿。然后再以见告。切勿广引疑似之说。以乱其实。恐益支离无益而反为害也。如何如何。来谕曰云云
来示云朱子于性情。用分域字。今言兼理气之性而谓之与天理有界分者。恐无不可。此说未安。盖情虽是性之发。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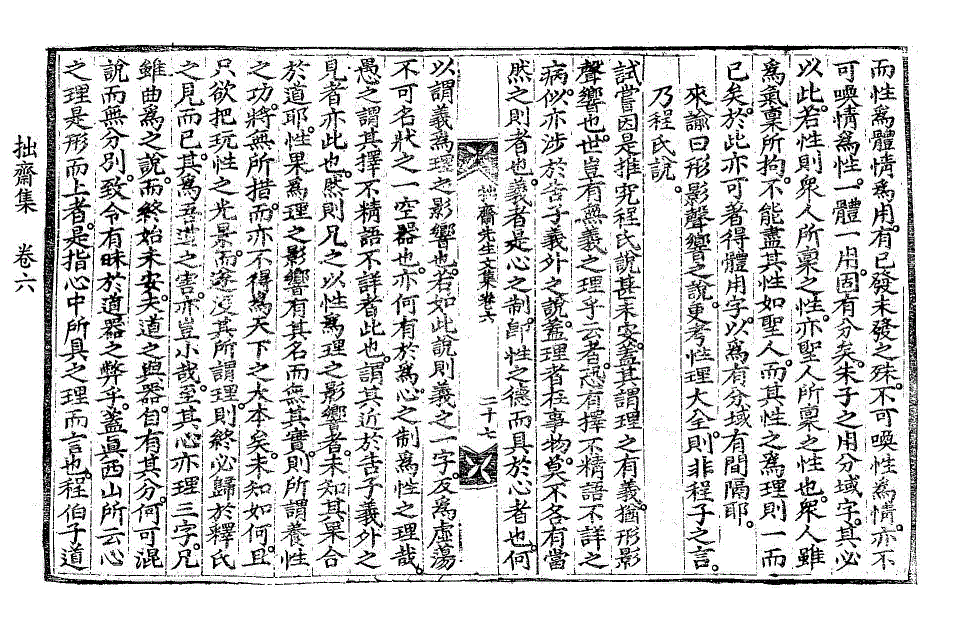 而性为体情为用。有已发未发之殊。不可唤性为情。亦不可唤情为性。一体一用。固有分矣。朱子之用分域字。其必以此。若性则众人所禀之性。亦圣人所禀之性也。众人虽为气禀所拘。不能尽其性如圣人。而其性之为理则一而已矣。于此亦可著得体用字。以为有分域有间隔耶。
而性为体情为用。有已发未发之殊。不可唤性为情。亦不可唤情为性。一体一用。固有分矣。朱子之用分域字。其必以此。若性则众人所禀之性。亦圣人所禀之性也。众人虽为气禀所拘。不能尽其性如圣人。而其性之为理则一而已矣。于此亦可著得体用字。以为有分域有间隔耶。来谕曰形影声响之说。更考性理大全。则非程子之言。乃程氏说。
试尝因是推究程氏说甚未安。盖其谓理之有义。犹形影声响也。世岂有无义之理乎云者。恐有择不精语不详之病。似亦涉于告子义外之说。盖理者在事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者也。义者是心之制。即性之德而具于心者也。何以谓义为理之影响也。若如此说则义之一字。反为虚荡不可名状之一空器也。亦何有于为心之制为性之理哉。愚之谓其择不精语不详者此也。谓其近于告子义外之见者亦此也。然则兄之以性为理之影响者。未知其果合于道耶。性果为理之影响有其名而无其实。则所谓养性之功。将无所措。而亦不得为天下之大本矣。未知如何。且只欲把玩性之光景。而遂没其所谓理。则终必归于释氏之见而已。其为吾道之害。亦岂小哉。至其心亦理三字。兄虽曲为之说。而终始未安。夫道之与器。自有其分。何可混说而无分别。致令有昧于道器之弊乎。盖真西山所云心之理是形而上者。是指心中所具之理而言也。程伯子道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7L 页
 即器器即道者。亦以理气之相须不相离而言。故曰一而二二而一。此果认道为器认器为道之言乎。苟令器亦道则只消一个一字以断之。何以曰一而二二而一乎。故愚之于前书。谓其施之于理气之说则可。施之于性理之说则不可者以此言也。如何如何。大槩性理之说。微而难知。苟未信及则不如两家各相拨置多少闲争竞。惟于日用间切己之病。近而易知处。共相勉励。至于久而或有少进焉。则庶几有益于身心。不为空言无实之归。性在相与加之意而已。如何如何。
即器器即道者。亦以理气之相须不相离而言。故曰一而二二而一。此果认道为器认器为道之言乎。苟令器亦道则只消一个一字以断之。何以曰一而二二而一乎。故愚之于前书。谓其施之于理气之说则可。施之于性理之说则不可者以此言也。如何如何。大槩性理之说。微而难知。苟未信及则不如两家各相拨置多少闲争竞。惟于日用间切己之病。近而易知处。共相勉励。至于久而或有少进焉。则庶几有益于身心。不为空言无实之归。性在相与加之意而已。如何如何。与金重卿别纸
近见朱子答郑子上书曰。气不可谓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性与气质杂而言之。非以气为性命云云。得是说然后益信鄙见之不谬。请更以兄所举珠在水中之喻明之。盖珠譬则性也。水譬则气质也。明月者。天下至洁之珠也。济水者。天下至清之水也。今以至洁之珠。置诸至清之水。则必莹澈而无瑕。未知此珠之至洁者。是珠之本体然耶。抑此珠之洁。犹有未尽。必待得水之清然后方有所增益。变其旧而为洁者耶。且以此珠之在浊水者。谓其本自不洁而然者耶。所遭之水虽殊而其为珠则一也。苟能知其虽在水中。而其本体之洁。初不以水之清浊而有所加损。则其不可以水为主而论珠。亦可知矣。其本末轻重之所在。不其较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8H 页
 然明甚矣乎。且以珠之在清水浊水之中者言之。则犹为有此珠彼珠之别也。若以此珠之在清水者。移置于浊水之中。旋复取出洗而濯之。还投于清水之中。则此珠之洁宜若无少损于初。然则其所以或清或浊者。水也非珠也。珠之洁固自若也。水之清浊。何能为加损于此珠本体之洁哉。今徒见珠之在浊水之中为浊水所掩。其洁不能自见于外。遂以浊水为主而言之。乃谓珠之性固然。则是见水而不见珠也。水反为重。珠反为轻。水能命珠而珠不能命水。澄治之功。亦无所施。然则先儒以珠喻性之意。果将何所准明以为用力之地乎。况离珠与洁而分二之。置界分于其间。则珠失其所以珠。而其所谓洁者。亦无所附以为洁。无乃不成说话耶。且不以珠之在清水之内者为准而言。以明珠本体之洁。而乃取浊滓不清之水掩珠之洁者以论其珠。则此乃徒循其末而昧其本者也。亦岂为能知珠者哉。以此推之则与今之言性而徒见性与气质之不相离。不以性为主。反归重于气质。以汩性之体段。使其有掩昧不明之弊。且以理字分而别之于性。以理归之天。以性归之人。以为有间有界分者。何以异也。若果如此则天与人。一彼一此。各有所主。有若不相交涉。只可任气质所禀之厚薄清浊。听其为圣为贤为愚为不肖而足矣。其善其恶。一定而不可易。圣人亦何贵于变化气质之功乎。惟其如此。故老先生于天命图说论性命处。乃曰四德五
然明甚矣乎。且以珠之在清水浊水之中者言之。则犹为有此珠彼珠之别也。若以此珠之在清水者。移置于浊水之中。旋复取出洗而濯之。还投于清水之中。则此珠之洁宜若无少损于初。然则其所以或清或浊者。水也非珠也。珠之洁固自若也。水之清浊。何能为加损于此珠本体之洁哉。今徒见珠之在浊水之中为浊水所掩。其洁不能自见于外。遂以浊水为主而言之。乃谓珠之性固然。则是见水而不见珠也。水反为重。珠反为轻。水能命珠而珠不能命水。澄治之功。亦无所施。然则先儒以珠喻性之意。果将何所准明以为用力之地乎。况离珠与洁而分二之。置界分于其间。则珠失其所以珠。而其所谓洁者。亦无所附以为洁。无乃不成说话耶。且不以珠之在清水之内者为准而言。以明珠本体之洁。而乃取浊滓不清之水掩珠之洁者以论其珠。则此乃徒循其末而昧其本者也。亦岂为能知珠者哉。以此推之则与今之言性而徒见性与气质之不相离。不以性为主。反归重于气质。以汩性之体段。使其有掩昧不明之弊。且以理字分而别之于性。以理归之天。以性归之人。以为有间有界分者。何以异也。若果如此则天与人。一彼一此。各有所主。有若不相交涉。只可任气质所禀之厚薄清浊。听其为圣为贤为愚为不肖而足矣。其善其恶。一定而不可易。圣人亦何贵于变化气质之功乎。惟其如此。故老先生于天命图说论性命处。乃曰四德五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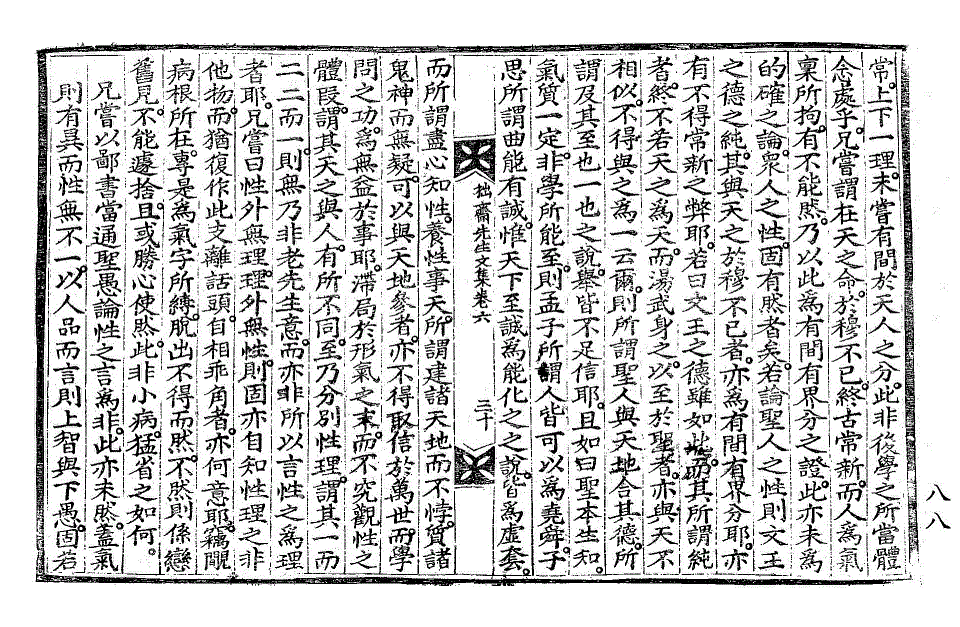 常。上下一理。未尝有间于天人之分。此非后学之所当体念处乎。兄尝谓在天之命。于穆不已。终古常新。而人为气禀所拘。有不能然。乃以此为有间有界分之證。此亦未为的确之论。众人之性。固有然者矣。若论圣人之性则文王之德之纯。其与天之于穆不已者。亦为有间有界分耶。亦有不得常新之弊耶。若曰文王之德虽如此。而其所谓纯者。终不若天之为天。而汤武身之。以至于圣者。亦与天不相似。不得与之为一云尔。则所谓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所谓及其至也一也之说。举皆不足信耶。且如曰圣本生知。气质一定。非学所能至。则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子思所谓曲能有诚。惟天下至诚为能化之之说。皆为虚套。而所谓尽心知性。养性事天。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可以与天地参者。亦不得取信于万世。而学问之功。为无益于事耶。滞局于形气之末。而不究观性之体段。谓其天之与人。有所不同。至乃分别性理。谓其一而二二而一。则无乃非老先生意。而亦非所以言性之为理者耶。兄尝曰性外无理。理外无性。则固亦自知性理之非他物。而犹复作此支离话头。自相乖角者。亦何意耶。窃覸病根所在。专是为气字所缚。脱出不得而然。不然则系恋旧见。不能遽舍。且或胜心使然。此非小病。猛省之如何。
常。上下一理。未尝有间于天人之分。此非后学之所当体念处乎。兄尝谓在天之命。于穆不已。终古常新。而人为气禀所拘。有不能然。乃以此为有间有界分之證。此亦未为的确之论。众人之性。固有然者矣。若论圣人之性则文王之德之纯。其与天之于穆不已者。亦为有间有界分耶。亦有不得常新之弊耶。若曰文王之德虽如此。而其所谓纯者。终不若天之为天。而汤武身之。以至于圣者。亦与天不相似。不得与之为一云尔。则所谓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所谓及其至也一也之说。举皆不足信耶。且如曰圣本生知。气质一定。非学所能至。则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子思所谓曲能有诚。惟天下至诚为能化之之说。皆为虚套。而所谓尽心知性。养性事天。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可以与天地参者。亦不得取信于万世。而学问之功。为无益于事耶。滞局于形气之末。而不究观性之体段。谓其天之与人。有所不同。至乃分别性理。谓其一而二二而一。则无乃非老先生意。而亦非所以言性之为理者耶。兄尝曰性外无理。理外无性。则固亦自知性理之非他物。而犹复作此支离话头。自相乖角者。亦何意耶。窃覸病根所在。专是为气字所缚。脱出不得而然。不然则系恋旧见。不能遽舍。且或胜心使然。此非小病。猛省之如何。兄尝以鄙书当通圣愚论性之言为非。此亦未然。盖气则有异而性无不一。以人品而言则上智与下愚。固若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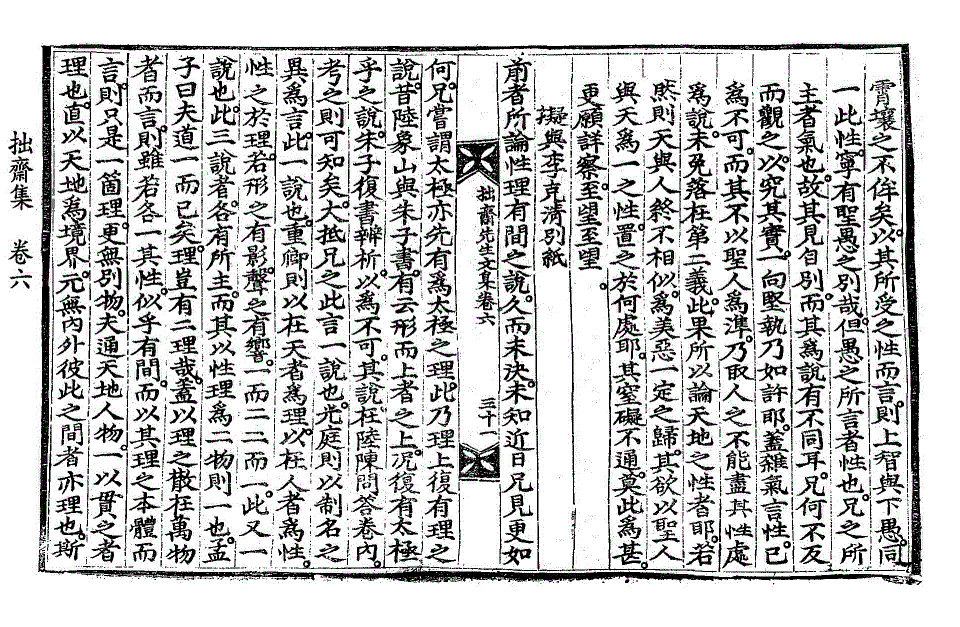 霄壤之不侔矣。以其所受之性而言。则上智与下愚。同一此性。宁有圣愚之别哉。但愚之所言者性也。兄之所主者气也。故其见自别。而其为说有不同耳。兄何不反而观之。以究其实。一向坚执乃如许耶。盖杂气言性。已为不可。而其不以圣人为准。乃取人之不能尽其性处为说。未免落在第二义。此果所以论天地之性者耶。若然则天与人终不相似。为美恶一定之归。其欲以圣人与天为一之性。置之于何处耶。其窒碍不通。莫此为甚。更愿详察。至望至望。
霄壤之不侔矣。以其所受之性而言。则上智与下愚。同一此性。宁有圣愚之别哉。但愚之所言者性也。兄之所主者气也。故其见自别。而其为说有不同耳。兄何不反而观之。以究其实。一向坚执乃如许耶。盖杂气言性。已为不可。而其不以圣人为准。乃取人之不能尽其性处为说。未免落在第二义。此果所以论天地之性者耶。若然则天与人终不相似。为美恶一定之归。其欲以圣人与天为一之性。置之于何处耶。其窒碍不通。莫此为甚。更愿详察。至望至望。拟与李克清别纸
前者所论性理有间之说。久而未决。未知近日兄见更如何。兄尝谓太极亦先有为太极之理。此乃理上复有理之说。昔陆象山与朱子书。有云形而上者之上。况复有太极乎之说。朱子复书辨析。以为不可。其说在陆陈问答卷内。考之则可知矣。大抵兄之此言一说也。光庭则以制名之异为言。此一说也。重卿则以在天者为理。以在人者为性。性之于理。若形之有影。声之有响。一而二二而一。此又一说也。此三说者。各有所主。而其以性理为二物则一也。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理岂有二理哉。盖以理之散在万物者而言。则虽若各一其性。似乎有间。而以其理之本体而言。则只是一个理。更无别物。夫通天地人物。一以贯之者理也。直以天地为境界。元无内外彼此之间者亦理也。斯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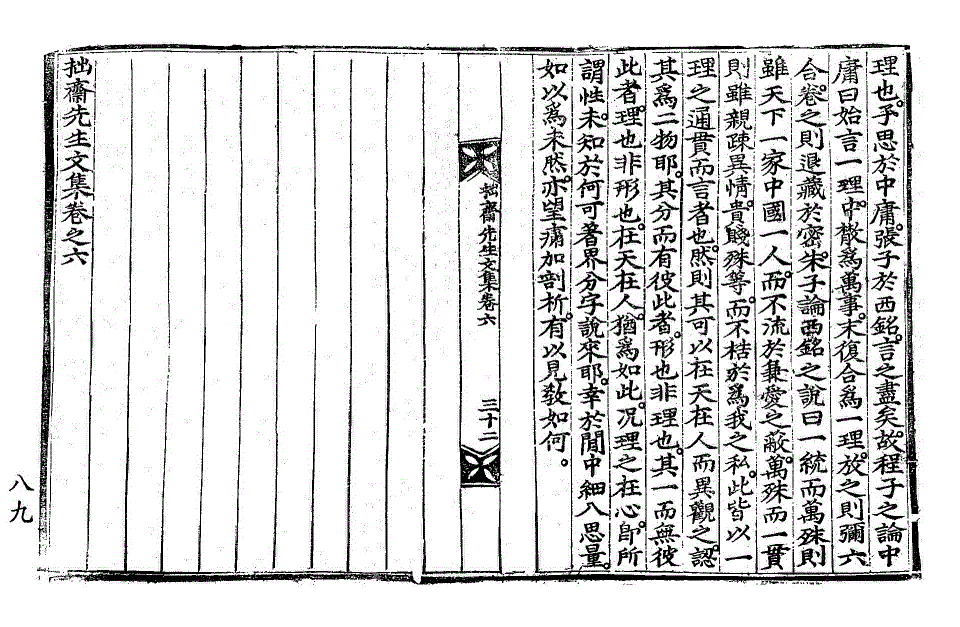 理也。子思于中庸。张子于西铭。言之尽矣。故程子之论中庸曰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子论西铭之说曰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殊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皆以一理之通贯而言者也。然则其可以在天在人而异观之。认其为二物耶。其分而有彼此者。形也非理也。其一而无彼此者。理也非形也。在天在人。犹为如此。况理之在心。即所谓性。未知于何可著界分字说来耶。幸于閒中细入思量。如以为未然。亦望痛加剖析。有以见教如何。
理也。子思于中庸。张子于西铭。言之尽矣。故程子之论中庸曰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子论西铭之说曰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殊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皆以一理之通贯而言者也。然则其可以在天在人而异观之。认其为二物耶。其分而有彼此者。形也非理也。其一而无彼此者。理也非形也。在天在人。犹为如此。况理之在心。即所谓性。未知于何可著界分字说来耶。幸于閒中细入思量。如以为未然。亦望痛加剖析。有以见教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