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x 页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书
书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4H 页
 与堂弟子强(千之)别纸
与堂弟子强(千之)别纸韩文公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朱子曰凡读书。不可倒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缓视微吟。熟读成诵。若不成诵。终不能有所得。又曰但就古圣贤言语。著实依其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长。又曰不必先立凡例。但熟读平看。从容讽咏。积久自当见得好处也。又曰如今朋友就文义上说。只恐未曾反身真个识得。故无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闲说话。不济事耳。又曰圣人之教。循循有序。不过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开其讲学之端。约之以礼。以严其践履之实。使之得寸则守其寸。得尺则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后道之全体。乃有所向望而渐可识。有所循习而渐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毙而后已。而其所造之浅深。所就之广狭。亦非可以必诣而可期。故夫子尝以先难后获为仁。又以先事后得为崇德。盖于此少差则心失其正。虽有钻坚仰高之志。而反为谋利计功之私矣。又曰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覆详玩。为有功耳。又曰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闲看过。直须是置心平淡悫实之地。玩味探索。虚恬省事以养之。持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切。不可以轻易急迫之心。求朝夕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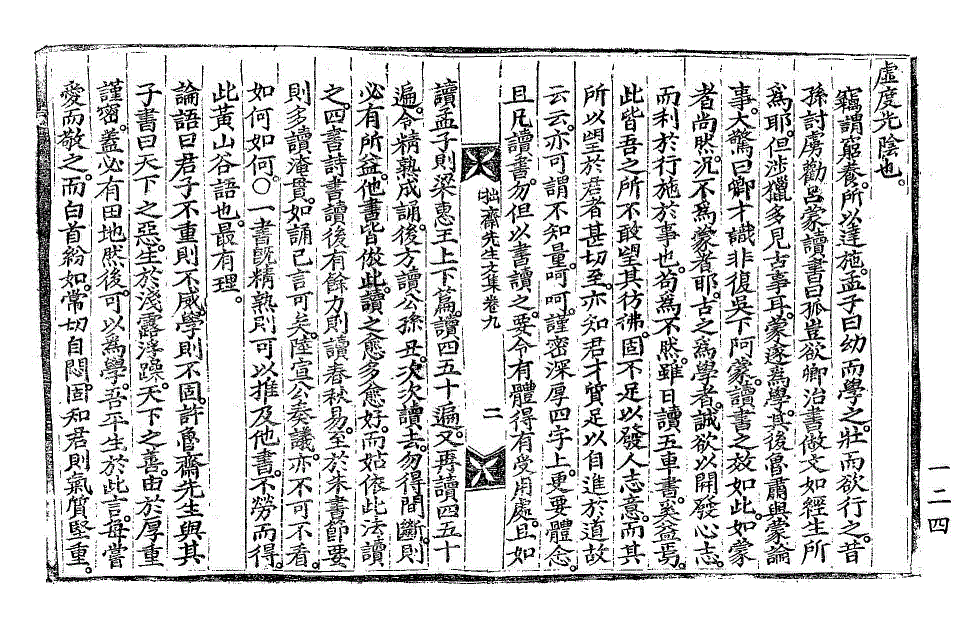 虚度光阴也。
虚度光阴也。窃谓穷养。所以达施。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昔孙讨虏劝吕蒙读书曰孤岂欲卿治书做文如经生所为耶。但涉猎多见古事耳。蒙遂为学。其后鲁肃与蒙论事。大惊曰卿才识非复吴下阿蒙。读书之效如此。如蒙者尚然。况不为蒙者耶。古之为学者。诚欲以开发心志。而利于行施于事也。苟为不然。虽日读五车书。奚益焉。此皆吾之所不敢望其彷佛。固不足以发人志意。而其所以望于君者甚切至。亦知君才质足以自进于道故云云。亦可谓不知量。呵呵。谨密深厚四字上。更要体念。且凡读书。勿但以书读之。要令有体得有受用处。且如读孟子则梁惠王上下篇。读四五十遍。又再读四五十遍。令精熟成诵。后方读公孙丑。次次读去。勿得间断。则必有所益。他书皆仿此。读之愈多愈好。而姑依此法读之。四书诗书读后有馀力则读春秋易。至于朱书节要则多读淹贯。如诵己言可矣。陆宣公奏议。亦不可不看。如何如何。○一书既精熟则可以推及他书。不劳而得。此黄山谷语也。最有理。
论语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许鲁斋先生与其子书曰天下之恶。生于浅露浮躁。天下之善。由于厚重谨密。盖必有田地然后。可以为学。吾平生于此言。每尝爱而敬之。而白首纷如。常切自闷。固知君则气质坚重。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5H 页
 而更以此勖之。乃缱绻在不谖之意也。如何如何。
而更以此勖之。乃缱绻在不谖之意也。如何如何。与子强书
近有人来言。在京闻一钜公谈君之美不置。早晚似当大用。而自叹无力可推挽云。闻来为之夜不能寐者数日。因复思之。以为凡人之所以自信而应时需。无失望于人实难。曾见祖考府君与徐监司仁元书。有曰人臣受恩非难。而报恩为难。爵位愈高而责任愈重。此实至训也。未知君将何修而待其求哉。方今 圣君在上。忧劳之意。每切于宵旰。而膏泽不下。国事日非。如不可须臾支吾。若此者何也。诚以奉行之人。无有以古昔圣王去邪听谏正心出治之道。告于 王前。以祛其蔽而然也。此必格君之大人。积其诚意。感动 上听。然后庶几其有济。固非声音笑貌所可为也。尝见朱夫子与陈侍郎书。以汲汲焉勉于大人之事。成己成物为说。又以不可但恃资质之美。告当路之人。劝其先自治。盖必在我有可据田地有可以及人。然后可以推行。方为有益于人国家故也。君气质厚重坚固。临事有定力。此固足以当大用。而又不可不加修为之功。鄙意欲望君于閒暇时。亲近书册。究观古圣贤用意之如何。而日检其身。益勉其所不及。益求其所未至。使义利公私之分。瞭然于心目之间。而于是非取舍之决。皆有以识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察之日益精。持之日益固。无所间断。久而熟之。至于有得。心与事一。则出而应世。亦必无难处之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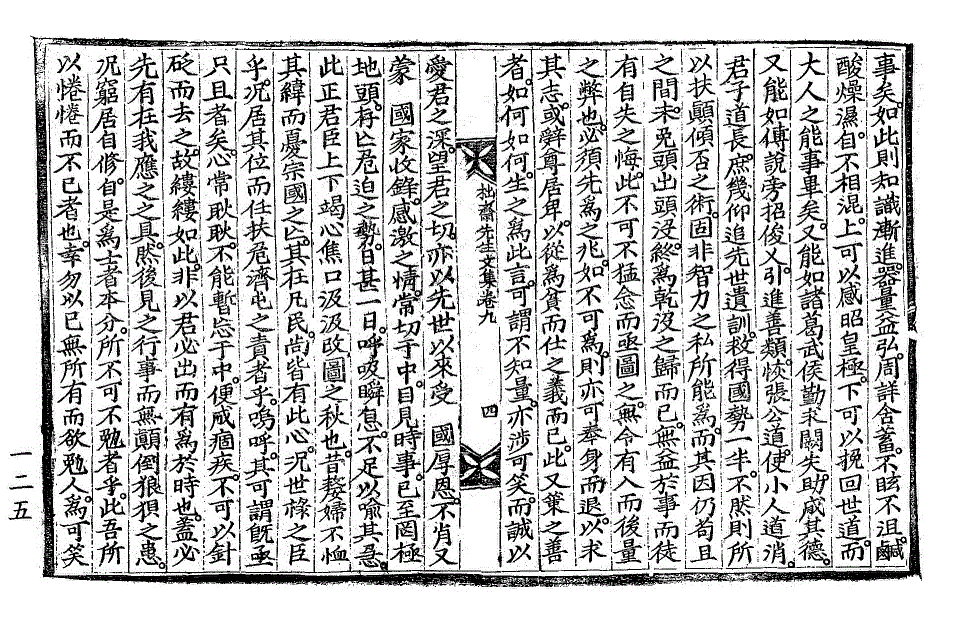 事矣。如此则知识渐进。器量益弘。周详含蓄。不眩不沮。咸酸燥湿。自不相混。上可以感昭皇极。下可以挽回世道。而大人之能事毕矣。又能如诸葛武侯勤求阙失。助成其德。又能如傅说旁招俊乂。引进善类。恢张公道。使小人道消。君子道长。庶几仰追先世遗训。救得国势一半。不然则所以扶颠倾否之术。固非智力之私所能为。而其因仍苟且之间。未免头出头没。终为乾没之归而已。无益于事而徒有自失之悔。此不可不猛念而亟图之。无令有入而后量之弊也。必须先为之兆。如不可为。则亦可奉身而退。以求其志。或辞尊居卑。以从为贫而仕之义而已。此又策之善者。如何如何。生之为此言。可谓不知量。亦涉可笑。而诚以爱君之深。望君之切。亦以先世以来受 国厚恩。不肖又蒙 国家收录。感激之情。常切于中。目见时事。已至罔极地头。存亡危迫之势。日甚一日。呼吸瞬息。不足以喻其急。此正君臣上下竭心焦口汲汲改图之秋也。昔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国之亡。其在凡民。尚皆有此心。况世禄之臣乎。况居其位而任扶危济屯之责者乎。呜呼。其可谓既亟只且者矣。心常耿耿。不能暂忘于中。便成痼疾。不可以针砭而去之。故缕缕如此。非以君必出而有为于时也。盖必先有在我应之之具。然后见之行事而无颠倒狼狈之患。况穷居自修。自是为士者本分。所不可不勉者乎。此吾所以惓惓而不已者也。幸勿以己无所有而欲勉人。为可笑
事矣。如此则知识渐进。器量益弘。周详含蓄。不眩不沮。咸酸燥湿。自不相混。上可以感昭皇极。下可以挽回世道。而大人之能事毕矣。又能如诸葛武侯勤求阙失。助成其德。又能如傅说旁招俊乂。引进善类。恢张公道。使小人道消。君子道长。庶几仰追先世遗训。救得国势一半。不然则所以扶颠倾否之术。固非智力之私所能为。而其因仍苟且之间。未免头出头没。终为乾没之归而已。无益于事而徒有自失之悔。此不可不猛念而亟图之。无令有入而后量之弊也。必须先为之兆。如不可为。则亦可奉身而退。以求其志。或辞尊居卑。以从为贫而仕之义而已。此又策之善者。如何如何。生之为此言。可谓不知量。亦涉可笑。而诚以爱君之深。望君之切。亦以先世以来受 国厚恩。不肖又蒙 国家收录。感激之情。常切于中。目见时事。已至罔极地头。存亡危迫之势。日甚一日。呼吸瞬息。不足以喻其急。此正君臣上下竭心焦口汲汲改图之秋也。昔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国之亡。其在凡民。尚皆有此心。况世禄之臣乎。况居其位而任扶危济屯之责者乎。呜呼。其可谓既亟只且者矣。心常耿耿。不能暂忘于中。便成痼疾。不可以针砭而去之。故缕缕如此。非以君必出而有为于时也。盖必先有在我应之之具。然后见之行事而无颠倒狼狈之患。况穷居自修。自是为士者本分。所不可不勉者乎。此吾所以惓惓而不已者也。幸勿以己无所有而欲勉人。为可笑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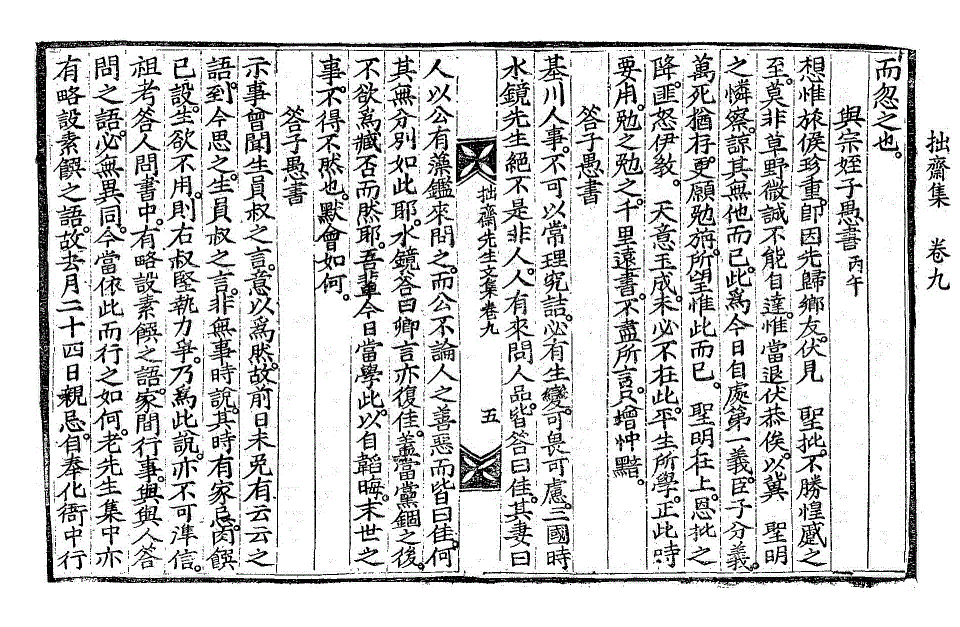 而忽之也。
而忽之也。与宗侄子愚书(丙午)
想惟旅候珍重。即因先归乡友。伏见 圣批。不胜惶蹙之至。莫非草野微诚不能自达。惟当退伏恭俟。以冀 圣明之怜察。谅其无他而已。此为今日自处第一义。臣子分义。万死犹存。更愿勉旃。所望惟此而已。 圣明在上。恩批之降。匪怒伊教。 天意玉成。未必不在此。平生所学。正此时要用。勉之勉之。千里远书。不尽所言。只增忡黯。
答子愚书
基川人事。不可以常理究诘。必有生变。可畏可虑。三国时水镜先生绝不是非人。人有来问人品。皆答曰佳。其妻曰人以公有藻鉴来问之。而公不论人之善恶而皆曰佳。何其无分别如此耶。水镜答曰卿言亦复佳。盖当党锢之后。不欲为臧否而然耶。吾辈今日当学此。以自韬晦。末世之事。不得不然也。默会如何。
答子愚书
示事曾闻生员叔之言。意以为然。故前日未免有云云之语。到今思之。生员叔之言。非无事时说。其时有家忌。肉馔已设。生欲不用。则右叔坚执力争。乃为此说。亦不可准信。祖考答人问书中。有略设素馔之语。家间行事。与与人答问之语。必无异同。今当依此而行之如何。老先生集中亦有略设素馔之语。故去月二十四日亲忌。自奉化衙中行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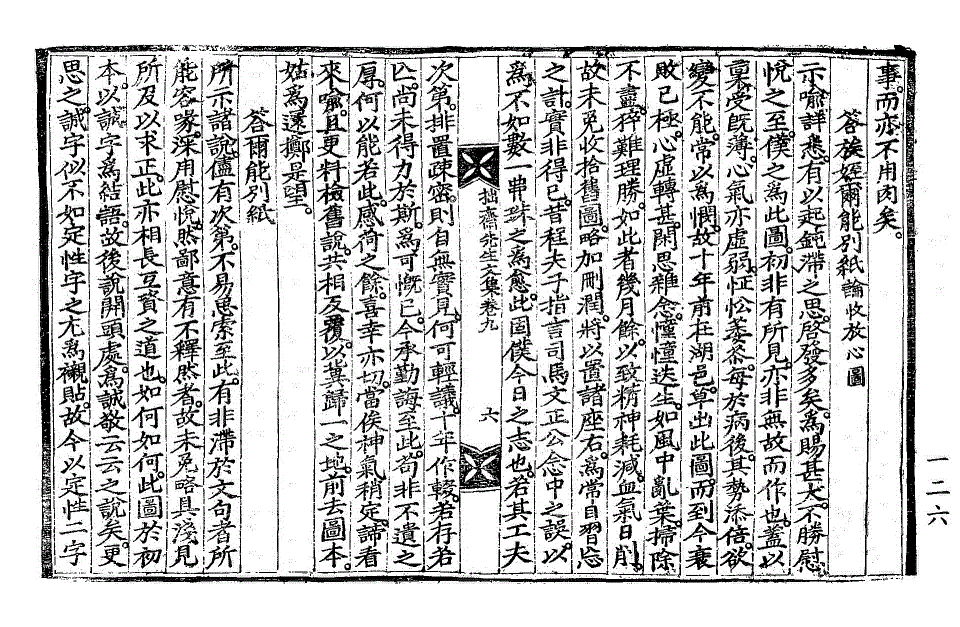 事。而亦不用肉矣。
事。而亦不用肉矣。答族侄尔能别纸(论收放心图)
示喻详悉。有以起钝滞之思。启发多矣。为赐甚大。不胜慰悦之至。仆之为此图。初非有所见。亦非无故而作也。盖以禀受既薄。心气亦虚弱。怔忪萎苶。每于病后。其势添倍。欲变不能。常以为悯。故十年前在湖邑。草出此图。而到今衰败已极。心虚转甚。闲思杂念。憧憧迭生。如风中乱叶。扫除不尽。猝难理胜。如此者几月馀。以致精神耗减。血气日削。故未免收拾旧图。略加删润。将以置诸座右。为常目习忘之计。实非得已。昔程夫子指言司马文正公念中之误。以为不如数一丳珠之为愈。此固仆今日之志也。若其工夫次第。排置疏密。则自无实见。何可轻议。十年作辍。若存若亡。尚未得力于斯。为可慨已。今承勤诲至此。苟非不遗之厚。何以能若此。感荷之馀。喜幸亦切。当俟神气稍定。谛看来喻。且更料检旧说。共相反覆。以冀归一之地。前去图本。姑为还掷是望。
答尔能别纸
所示诸说。尽有次第。不易思索至此。有非滞于文句者所能容喙。深用慰悦。然鄙意有不释然者。故未免略具浅见所及以求正。此亦相长互资之道也。如何如何。此图于初本。以诚字为结语。故后说开头处。为诚敬云云之说矣。更思之。诚字似不如定性字之尤为衬贴。故今以定性二字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7H 页
 易诚字。盖实心主敬。乃所以诚。虽不言诚。而诚在其中故也。既从今说则后说如自诚字。似无渐次。且其措语之间。又未免径约未圆之弊。故以朱子说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是心之主宰者改之。而其体之于身(止)以实其行十六字。诚如来喻之云。且似近于太担当为未安。故亦以所示之语易之。而就加点缀数个字。以足其意。未知于意如何。其又能以下则姑因存前说。以俟讲定何者。来喻所谓集义二字为剩云者。似为未然故也。盖居敬者。存心之属。集义者。明善之功。若但居敬而不集义。则为有体而无用。若集义而不本于敬。则本原无主。亦不能以明善。故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居敬集义不可偏废之说也。敬固兼动静。而集义包在动时工夫之内。不须更为提起者。信有如来喻之所云也。然鄙意以为理虽如此。而不如更为表出二字。以畅其意。然后尤为历落分明。且更完备。如何如何。况信乎以下云云。乃是申言上文之意。为结之之辞。则似不为架屋叠床之归。未知其果为剩语否耶。以图内所排置者而言之。则戒惧者存心之事。故以三贵附其下。慎独者明善之主。故以四勿附其下。是其三贵四勿者。乃戒惧慎独之所有事。而以此始以此终。合内外一动静。无乎不在者敬也。所谓主一无适以下诸说。皆敬字之注脚。初非有上下阶级之有方所有渐次。无由此至彼之可言。则三贵四勿者。又岂有层级彼此于其间哉。其所
易诚字。盖实心主敬。乃所以诚。虽不言诚。而诚在其中故也。既从今说则后说如自诚字。似无渐次。且其措语之间。又未免径约未圆之弊。故以朱子说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是心之主宰者改之。而其体之于身(止)以实其行十六字。诚如来喻之云。且似近于太担当为未安。故亦以所示之语易之。而就加点缀数个字。以足其意。未知于意如何。其又能以下则姑因存前说。以俟讲定何者。来喻所谓集义二字为剩云者。似为未然故也。盖居敬者。存心之属。集义者。明善之功。若但居敬而不集义。则为有体而无用。若集义而不本于敬。则本原无主。亦不能以明善。故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居敬集义不可偏废之说也。敬固兼动静。而集义包在动时工夫之内。不须更为提起者。信有如来喻之所云也。然鄙意以为理虽如此。而不如更为表出二字。以畅其意。然后尤为历落分明。且更完备。如何如何。况信乎以下云云。乃是申言上文之意。为结之之辞。则似不为架屋叠床之归。未知其果为剩语否耶。以图内所排置者而言之。则戒惧者存心之事。故以三贵附其下。慎独者明善之主。故以四勿附其下。是其三贵四勿者。乃戒惧慎独之所有事。而以此始以此终。合内外一动静。无乎不在者敬也。所谓主一无适以下诸说。皆敬字之注脚。初非有上下阶级之有方所有渐次。无由此至彼之可言。则三贵四勿者。又岂有层级彼此于其间哉。其所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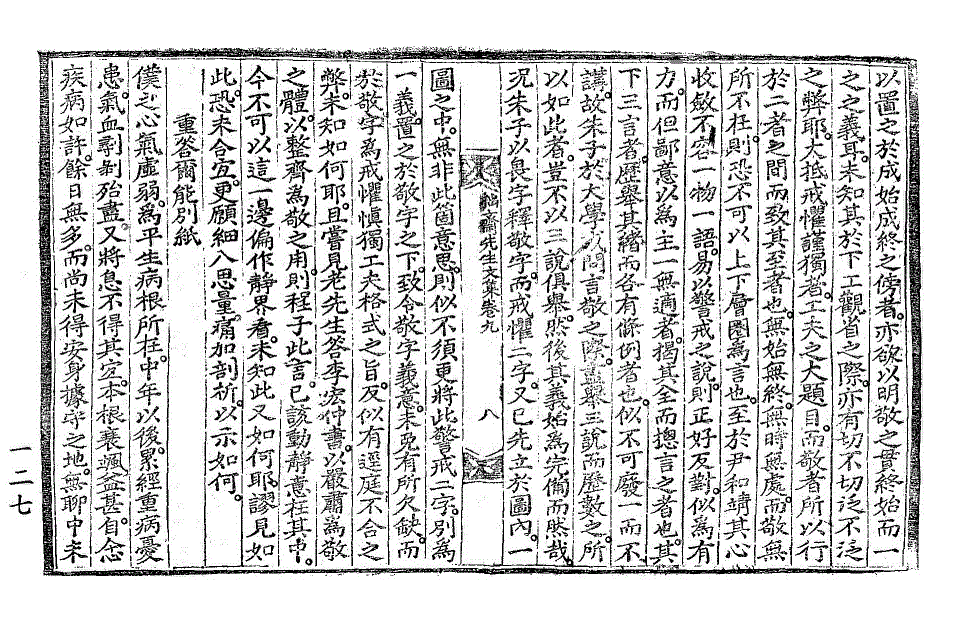 以置之于成始成终之傍者。亦欲以明敬之贯终始而一之之义耳。未知其于下工观省之际。亦有切不切泛不泛之弊耶。大抵戒惧谨独者。工夫之大题目。而敬者所以行于二者之间而致其至者也。无始无终。无时无处。而敬无所不在。则恐不可以上下层圈为言也。至于尹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一语。易以警戒之说。则正好反对。似为有力。而但鄙意以为主一无适者。揭其全而总言之者也。其下三言者。历举其绪而各有条例者也。似不可废一而不讲。故朱子于大学或问言敬之际。尽举三说而历数之。所以如此者。岂不以三说俱举。然后其义始为完备而然哉。况朱子以畏字释敬字。而戒惧二字。又已先立于图内。一图之中。无非此个意思。则似不须更将此警戒二字。别为一义。置之于敬字之下。致令敬字义意。未免有所欠缺。而于敬字为戒惧慎独工夫格式之旨。反似有径庭不合之弊。未知如何耶。且尝见老先生答李宏仲书。以严肃为敬之体。以整齐为敬之用。则程子此言。已该动静意在其中。今不可以这一边偏作静界看。未知此又如何耶。谬见如此。恐未合宜。更愿细入思量。痛加剖析。以示如何。
以置之于成始成终之傍者。亦欲以明敬之贯终始而一之之义耳。未知其于下工观省之际。亦有切不切泛不泛之弊耶。大抵戒惧谨独者。工夫之大题目。而敬者所以行于二者之间而致其至者也。无始无终。无时无处。而敬无所不在。则恐不可以上下层圈为言也。至于尹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一语。易以警戒之说。则正好反对。似为有力。而但鄙意以为主一无适者。揭其全而总言之者也。其下三言者。历举其绪而各有条例者也。似不可废一而不讲。故朱子于大学或问言敬之际。尽举三说而历数之。所以如此者。岂不以三说俱举。然后其义始为完备而然哉。况朱子以畏字释敬字。而戒惧二字。又已先立于图内。一图之中。无非此个意思。则似不须更将此警戒二字。别为一义。置之于敬字之下。致令敬字义意。未免有所欠缺。而于敬字为戒惧慎独工夫格式之旨。反似有径庭不合之弊。未知如何耶。且尝见老先生答李宏仲书。以严肃为敬之体。以整齐为敬之用。则程子此言。已该动静意在其中。今不可以这一边偏作静界看。未知此又如何耶。谬见如此。恐未合宜。更愿细入思量。痛加剖析。以示如何。重答尔能别纸
仆之心气虚弱。为平生病根所在。中年以后。累经重病忧患。气血𠟢剥殆尽。又将息不得其宜。本根衰飒益甚。自念疾病如许。馀日无多。而尚未得安身据守之地。无聊中未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8H 页
 免为此图。其意只欲救目前之病。为未死前冷淡活计而已。岂能出入古训。对同勘合。如来喻之所云也。至其所示末端云云之语。不似太甚。吾辈閒里互相劘切。胥匡求益之道。断不如此。胡乃尔耶。使外人闻之。岂不重为老拙诟病。惹得嘲笑。而于吾君自处待人之道。亦未为善谅之如何。图中曾以三贵四勿。置之于敬说末端者。以为戒惧谨独。为工夫之大体。而所谓敬者。实在其间为终始。故意其如此排置。似为无妨。前书所云。盖以此也。今见来示。因复筹思。始觉来说为长。乃以三贵四勿。合内外一动静四个名目。互换而易置之。反而观之。则三贵四勿。正在敬字范围之内。融贯吻合。自不相离。而合内外一动静者。又移在下方。与成始成终字。共为总结之辞。转见位置齐整。各从其类。前日芥滞之病。一时消遣都尽。开阔通畅。为益弘大。往复讲说之不可无如此。而贵见之精审。有非老拙钝滞所及。慰悦之馀。幸荷亦深。此图之能为有无得失。虽不可知。而吾辈即今所见。既与相符。幸无异同。则亦可因诸君彊辅。庶几少变气质。有所发明否耶。更愿胥教诲胥策勉。无忘今日之意。幸甚幸甚。
免为此图。其意只欲救目前之病。为未死前冷淡活计而已。岂能出入古训。对同勘合。如来喻之所云也。至其所示末端云云之语。不似太甚。吾辈閒里互相劘切。胥匡求益之道。断不如此。胡乃尔耶。使外人闻之。岂不重为老拙诟病。惹得嘲笑。而于吾君自处待人之道。亦未为善谅之如何。图中曾以三贵四勿。置之于敬说末端者。以为戒惧谨独。为工夫之大体。而所谓敬者。实在其间为终始。故意其如此排置。似为无妨。前书所云。盖以此也。今见来示。因复筹思。始觉来说为长。乃以三贵四勿。合内外一动静四个名目。互换而易置之。反而观之。则三贵四勿。正在敬字范围之内。融贯吻合。自不相离。而合内外一动静者。又移在下方。与成始成终字。共为总结之辞。转见位置齐整。各从其类。前日芥滞之病。一时消遣都尽。开阔通畅。为益弘大。往复讲说之不可无如此。而贵见之精审。有非老拙钝滞所及。慰悦之馀。幸荷亦深。此图之能为有无得失。虽不可知。而吾辈即今所见。既与相符。幸无异同。则亦可因诸君彊辅。庶几少变气质。有所发明否耶。更愿胥教诲胥策勉。无忘今日之意。幸甚幸甚。寄儿辈别纸(丁丑)
余禀性昏塞。懦弱尤甚。随事废弛。不能主张。而自幼多病。又因丧患积忧伤心。失学至此。虽时有警省开发之时。而旋复闭锢。乍存乍亡。行年四十。无一可观。中夜念至。不觉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8L 页
 感泪交集。玆录数语。以与儿辈共之。庶母曰徒言无益。父子兄弟。共相劝勉。共相规警。补其不及。以冀万一。则庶无大过。以终其身。区区至心。汝辈览之。老亲少婴忧患。重以贫穷。辛勤艰苦之状。难以尽言。年衰多病。已迫迟暮。无他子女。惟余一人。而不孝无状。无以奉承愉悦。以乐其心。情理极为哀痛。汝曹须日侍侧。和色婉容。怡怡为乐。虽甚难行之事。专以承顺为念。勉行无违。老人心弱。易以兴感。少有违拂。恐伤其志。古人有为弄雏驴鸣。以悦其心者。有将撤必问所与者。有为邻妪共设鱼脍。以养其志者。至于父母之所爱亦爱之。若婢仆犬马之类。无不敬且爱之。以顺适其意。孝子之无所不用其极如此。汝曹须知此意。更相体念。常令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可矣。汝父不孝。可以为戒。不可学也。
感泪交集。玆录数语。以与儿辈共之。庶母曰徒言无益。父子兄弟。共相劝勉。共相规警。补其不及。以冀万一。则庶无大过。以终其身。区区至心。汝辈览之。老亲少婴忧患。重以贫穷。辛勤艰苦之状。难以尽言。年衰多病。已迫迟暮。无他子女。惟余一人。而不孝无状。无以奉承愉悦。以乐其心。情理极为哀痛。汝曹须日侍侧。和色婉容。怡怡为乐。虽甚难行之事。专以承顺为念。勉行无违。老人心弱。易以兴感。少有违拂。恐伤其志。古人有为弄雏驴鸣。以悦其心者。有将撤必问所与者。有为邻妪共设鱼脍。以养其志者。至于父母之所爱亦爱之。若婢仆犬马之类。无不敬且爱之。以顺适其意。孝子之无所不用其极如此。汝曹须知此意。更相体念。常令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可矣。汝父不孝。可以为戒。不可学也。寄儿辈别纸(癸未)
凡今之士。皆留心于文辞利达之间。汲汲以决科名登显仕为期。不得则不戚戚于怀者鲜矣。吾意则不然。夫富贵利达。自有命物者处分。非可求而得之也。为士者惟当绝去外诱。从事于经书之训。以培本根。以广识见。内重者外物自不得不轻。存心修身。高可学古人。下亦不失为善士。自乐无忧。安分常足。其为富贵。孰加于是。若其风云月露之奇。雕刻肝肾。无益于性情。虽不学可也。汝辈年晚失学。今不可汎滥诸书。须专力于小学及四书中。熟读精思。以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9H 页
 冀得力。吾病已极。亲年又高。自今惟愿杜门却扫。与汝辈相守于寂寞之滨。时于温凊之暇。相与谈论糟粕。以终馀日。庶几赖天之灵。得免小人之归乎。聊记之。以与汝曹勖焉。
冀得力。吾病已极。亲年又高。自今惟愿杜门却扫。与汝辈相守于寂寞之滨。时于温凊之暇。相与谈论糟粕。以终馀日。庶几赖天之灵。得免小人之归乎。聊记之。以与汝曹勖焉。寄儿辈别纸
今人以年晚就学者。为必不可成。争聚而笑之。其人亦以此自沮。遂辍而不讲。此世人之通病也。古之人有三十馀始入学者。李初平年五十。犹问道于濂溪。二年而有得。由此观之。年无早晚。惟真诚向学为贵耳。虽才分有高下。所得有浅深。不得望古人之阃域。不犹愈于终不为者哉。苟能资于学。以寡其过。则虽不至于君子。得不为善人乎。况致一不已。则亦有可至之理耶。尝记古人之诗曰贫家好扫地。贫女好梳头。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余深有感于斯言。
又有一焉。为学之道。似当以沈潜涵蓄。内得于己为贵。若不能诚笃。而只将学之一字。虚立名称。未始一得。径自暴露于人。为人所笑。而卒无所益于身心。则不如不为之为愈。此亦不可不知也。吾与汝曹。盍相与戒之。
寄子宜河书
汝读论语几何。须日以二张或一张为限。精思熟读。切勿多学。亦勿急读。须静坐一室。缓视微吟。玩味循环。少其课程而多其读数。如此则可以完养精神。且心下安静。不奔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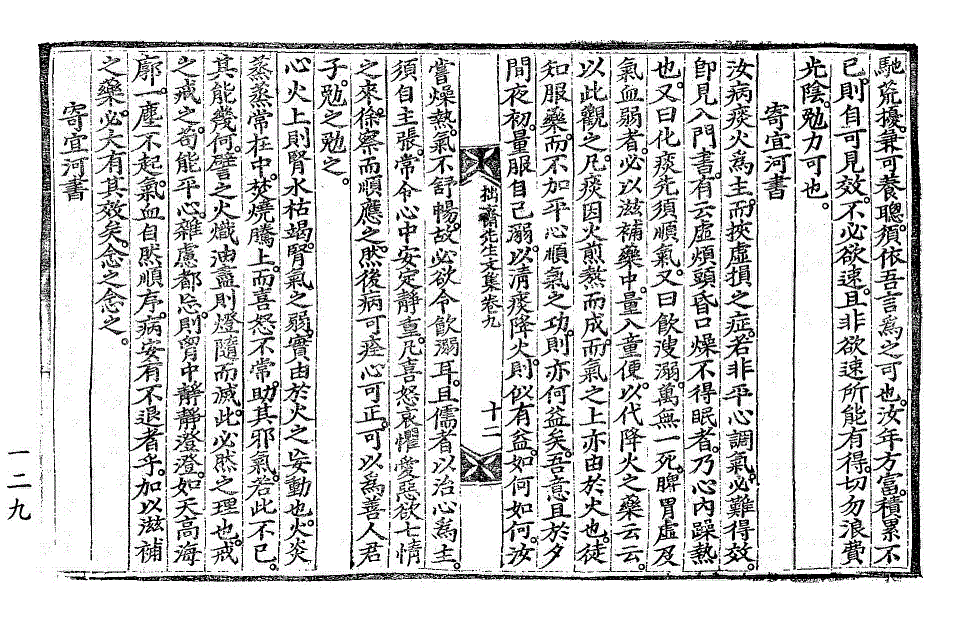 驰荒扰。兼可养聪。须依吾言为之可也。汝年方富。积累不已。则自可见效。不必欲速。且非欲速所能有得。切勿浪费光阴。勉力可也。
驰荒扰。兼可养聪。须依吾言为之可也。汝年方富。积累不已。则自可见效。不必欲速。且非欲速所能有得。切勿浪费光阴。勉力可也。寄宜河书
汝病痰火为主。而挟虚损之症。若非平心调气。必难得效。即见入门书。有云虚烦头昏口燥不得眠者。乃心内躁热也。又曰化痰先须顺气。又曰饮溲溺。万无一死。脾胃虚及气血弱者。必以滋补药中。量入童便。以代降火之药云云。以此观之。凡痰因火煎熬而成。而气之上亦由于火也。徒知服药。而不加平心顺气之功。则亦何益矣。吾意且于夕间夜初。量服自己溺。以清痰降火。则似有益。如何如何。汝尝燥热。气不舒畅。故必欲令饮溺耳。且儒者以治心为主。须自主张。常令心中安定静重。凡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之来。徐察而顺应之。然后病可痊心可正。可以为善人君子。勉之勉之。
心火上则肾水枯竭。肾气之弱。实由于火之妄动也。火炎蒸蒸常在中。焚烧腾上。而喜怒不常。助其邪气。若此不已。其能几何。譬之火炽油尽则灯随而灭。此必然之理也。戒之戒之。苟能平心杂虑都忘。则胸中静静澄澄。如天高海廓。一尘不起。气血自然顺序。病安有不退者乎。加以滋补之药。必大有其效矣。念之念之。
寄宜河书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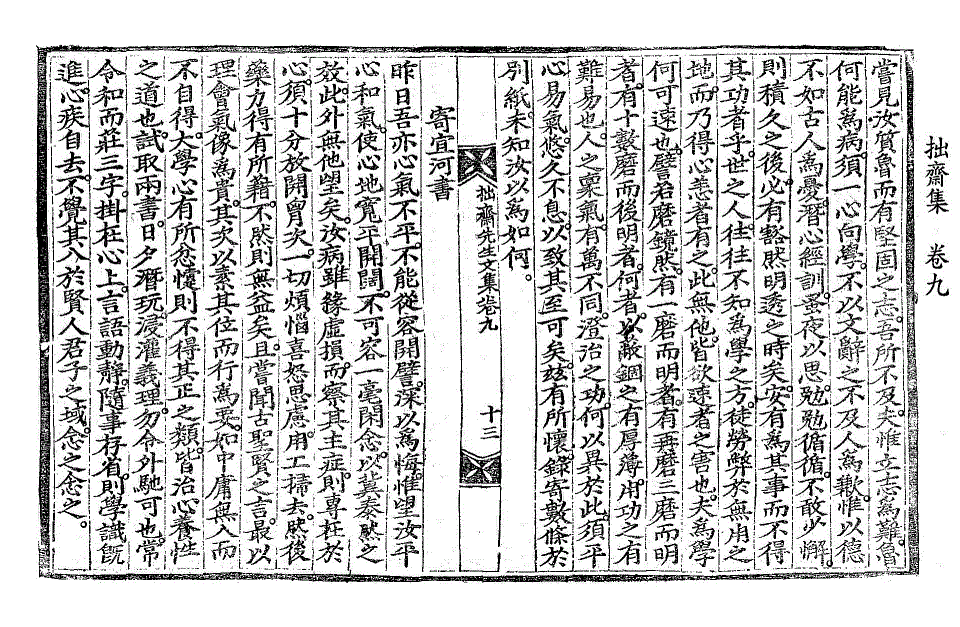 尝见汝质鲁而有坚固之志。吾所不及。夫惟立志为难。鲁何能为病。须一心向学。不以文辞之不及人为歉。惟以德不如古人为忧。潜心经训。蚤夜以思。勉勉循循。不敢少懈。则积久之后。必有豁然明透之时矣。安有为其事而不得其功者乎。世之人。往往不知为学之方。徒劳弊于无用之地。而乃得心恙者有之。此无他。皆欲速者之害也。夫为学何可速也。譬若磨镜然。有一磨而明者。有再磨三磨而明者。有十数磨而后明者。何者。以蔽锢之有厚薄。用功之有难易也。人之禀气。有万不同。澄治之功。何以异于此。须平心易气。悠久不息。以致其至可矣。玆有所怀。录寄数条于别纸。未知汝以为如何。
尝见汝质鲁而有坚固之志。吾所不及。夫惟立志为难。鲁何能为病。须一心向学。不以文辞之不及人为歉。惟以德不如古人为忧。潜心经训。蚤夜以思。勉勉循循。不敢少懈。则积久之后。必有豁然明透之时矣。安有为其事而不得其功者乎。世之人。往往不知为学之方。徒劳弊于无用之地。而乃得心恙者有之。此无他。皆欲速者之害也。夫为学何可速也。譬若磨镜然。有一磨而明者。有再磨三磨而明者。有十数磨而后明者。何者。以蔽锢之有厚薄。用功之有难易也。人之禀气。有万不同。澄治之功。何以异于此。须平心易气。悠久不息。以致其至可矣。玆有所怀。录寄数条于别纸。未知汝以为如何。寄宜河书
昨日吾亦心气不平。不能从容开譬。深以为悔。惟望汝平心和气。使心地宽平开阔。不可容一毫闲念。以冀泰然之效。此外无他望矣。汝病虽缘虚损。而察其主症。则专在于心。须十分放开胸次。一切烦恼喜怒思虑。用工扫去。然后药力得有所藉。不然则无益矣。且尝闻古圣贤之言。最以理会气像为贵。其次以素其位而行为要。如中庸无入而不自得。大学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之类。皆治心养性之道也。试取两书。日夕潜玩浸灌义理。勿令外驰可也。常令和而庄三字。挂在心上。言语动静。随事存省。则学识既进。心疾自去。不觉其入于贤人君子之域。念之念之。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0L 页
 所谓理会气象者。只是平其心易其气。其色也和而庄。其言辞也详而安。婉而正。其举止也不躁扰。记曰俨若思安定辞者。真可念也。心志坚定。先立其大者。则在外可善可怒可惊可怪可忧可怕一切烦恼之事。皆不在我。顾自省其身。无所可愧耳。如此则岂不心广体胖睟面盎背。优入于君子之域哉。不然而常令忿懥之念在中。自伤其天和。则心失其正。触处皆病。将为人世间弃物。哀哉。更宜著心思量。
所谓理会气象者。只是平其心易其气。其色也和而庄。其言辞也详而安。婉而正。其举止也不躁扰。记曰俨若思安定辞者。真可念也。心志坚定。先立其大者。则在外可善可怒可惊可怪可忧可怕一切烦恼之事。皆不在我。顾自省其身。无所可愧耳。如此则岂不心广体胖睟面盎背。优入于君子之域哉。不然而常令忿懥之念在中。自伤其天和。则心失其正。触处皆病。将为人世间弃物。哀哉。更宜著心思量。寄示儿辈别纸
昔马援寄兄子严敦书。诫其好议论人长短政治得失。以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为言。程子亦言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盖下讪上则无忠敬之心。又古人遗子弟书。不许言边报差除。州县官员得失。众人所作过恶。以为非但招灾。实能损德。前后圣贤之训。不啻丁宁如此。尔曹其各念之哉。君子自治不暇。何暇更有工夫可点检他人也。尝见小学书中。有胡安定公之门人。不论贤愚。皆循循雅饬。万石君之家。淳厚谨慎。不敢为非。此后世之所当法也。凡人例不能自检其身。而好议论人长短是非。至于妄论朝政得失。官员善恶。余甚病之。诗曰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我先世忠敬孝谨之风。各宜遵奉。无敢或踰。勉之勉之。
闻人之谤慎勿怒。闻人之誉慎勿喜。闻谤益自修。闻誉益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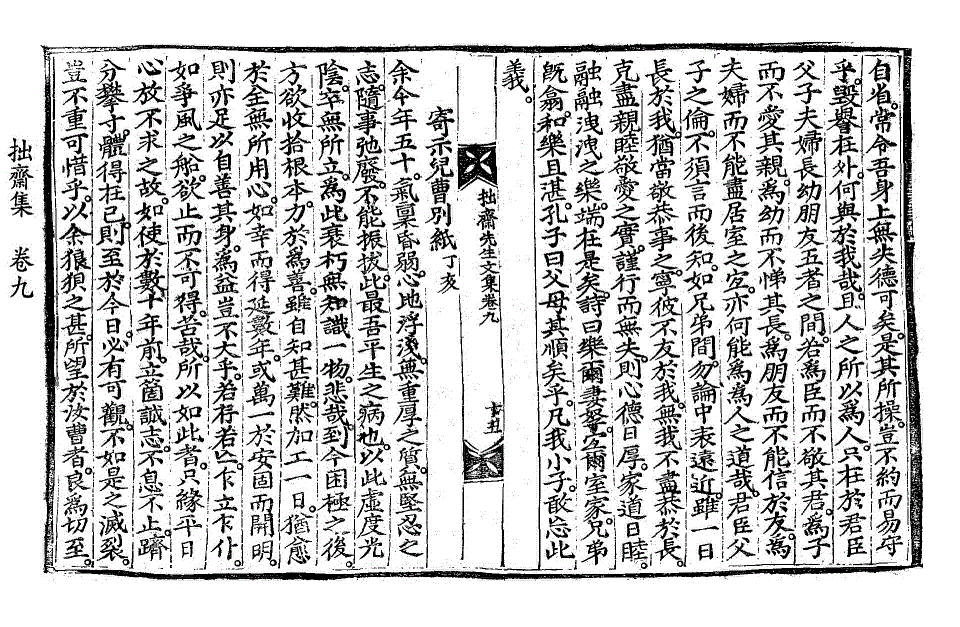 自省。常令吾身上无失德可矣。是其所操。岂不约而易守乎。毁誉在外。何与于我哉。且人之所以为人。只在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间。若为臣而不敬其君。为子而不爱其亲。为幼而不悌其长。为朋友而不能信于友。为夫妇而不能尽居室之宜。亦何能为为人之道哉。君臣父子之伦。不须言而后知。如兄弟间。勿论中表远近。虽一日长于我。犹当敬恭事之。宁彼不友于我。无我不尽恭于长。克尽亲睦敬爱之实。谨行而无失。则心德日厚。家道日睦。融融泄泄之乐。端在是矣。诗曰乐尔妻孥。宜尔室家。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孔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凡我小子。敢忘此义。
自省。常令吾身上无失德可矣。是其所操。岂不约而易守乎。毁誉在外。何与于我哉。且人之所以为人。只在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间。若为臣而不敬其君。为子而不爱其亲。为幼而不悌其长。为朋友而不能信于友。为夫妇而不能尽居室之宜。亦何能为为人之道哉。君臣父子之伦。不须言而后知。如兄弟间。勿论中表远近。虽一日长于我。犹当敬恭事之。宁彼不友于我。无我不尽恭于长。克尽亲睦敬爱之实。谨行而无失。则心德日厚。家道日睦。融融泄泄之乐。端在是矣。诗曰乐尔妻孥。宜尔室家。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孔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凡我小子。敢忘此义。寄示儿曹别纸(丁亥)
余今年五十。气禀昏弱。心地浮浅。无重厚之质。无坚忍之志。随事弛废。不能振拔。此最吾平生之病也。以此虚度光阴。卒无所立。为此衰朽无知识一物。悲哉。到今困极之后。方欲收拾根本。力于为善。虽自知甚难然加工一日。犹愈于全无所用心。如幸而得延数年。或万一于安固而开明。则亦足以自善其身。为益岂不大乎。若存若亡。乍立乍仆。如争风之船。欲止而不可得。苦哉。所以如此者。只缘平日心放不求之故。如使于数十年前。立个诚志。不息不止。跻分攀寸。体得在己。则至于今日。必有可观。不如是之灭裂。岂不重可惜乎。以余狼狈之甚。所望于汝曹者。良为切至。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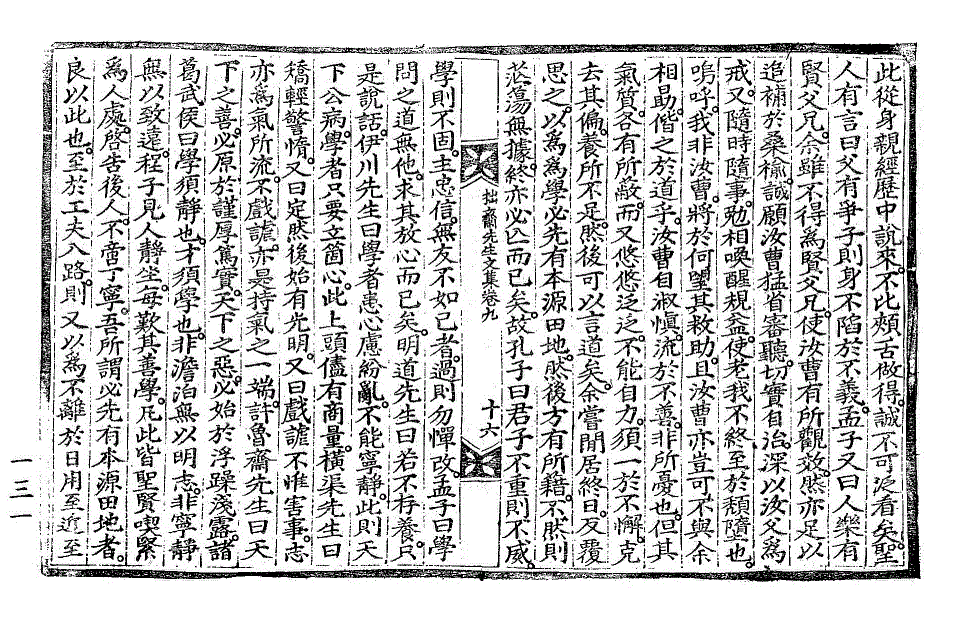 此从身亲经历中说来。不比颊舌做得。诚不可泛看矣。圣人有言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孟子又曰人乐有贤父兄。余虽不得为贤父兄。使汝曹有所观效。然亦足以追补于桑榆。诚愿汝曹猛省审听。切实自治。深以汝父为戒。又随时随事。勉相唤醒规益。使老我不终至于颓堕也。呜呼。我非汝曹。将于何望其救助。且汝曹亦岂可不与余相勖。偕之于道乎。汝曹自淑慎。流于不善。非所忧也。但其气质。各有所蔽。而又悠悠泛泛。不能自力。须一于不懈。克去其偏。养所不足。然后可以言道矣。余尝閒居终日。反覆思之。以为为学必先有本源田地。然后方有所藉。不然则茫荡无据。终亦必亡而已矣。故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明道先生曰若不存养。只是说话。伊川先生曰学者患心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公病。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横渠先生曰矫轻警惰。又曰定然后始有光明。又曰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气所流。不戏谑。亦是持气之一端。许鲁斋先生曰天下之善。必原于谨厚笃实。天下之恶。必始于浮躁浅露。诸葛武侯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程子见人静坐。每叹其善学。凡此皆圣贤吃紧为人处。启告后人。不啻丁宁。吾所谓必先有本源田地者。良以此也。至于工夫入路。则又以为不离于日用至近至
此从身亲经历中说来。不比颊舌做得。诚不可泛看矣。圣人有言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孟子又曰人乐有贤父兄。余虽不得为贤父兄。使汝曹有所观效。然亦足以追补于桑榆。诚愿汝曹猛省审听。切实自治。深以汝父为戒。又随时随事。勉相唤醒规益。使老我不终至于颓堕也。呜呼。我非汝曹。将于何望其救助。且汝曹亦岂可不与余相勖。偕之于道乎。汝曹自淑慎。流于不善。非所忧也。但其气质。各有所蔽。而又悠悠泛泛。不能自力。须一于不懈。克去其偏。养所不足。然后可以言道矣。余尝閒居终日。反覆思之。以为为学必先有本源田地。然后方有所藉。不然则茫荡无据。终亦必亡而已矣。故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明道先生曰若不存养。只是说话。伊川先生曰学者患心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公病。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横渠先生曰矫轻警惰。又曰定然后始有光明。又曰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气所流。不戏谑。亦是持气之一端。许鲁斋先生曰天下之善。必原于谨厚笃实。天下之恶。必始于浮躁浅露。诸葛武侯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程子见人静坐。每叹其善学。凡此皆圣贤吃紧为人处。启告后人。不啻丁宁。吾所谓必先有本源田地者。良以此也。至于工夫入路。则又以为不离于日用至近至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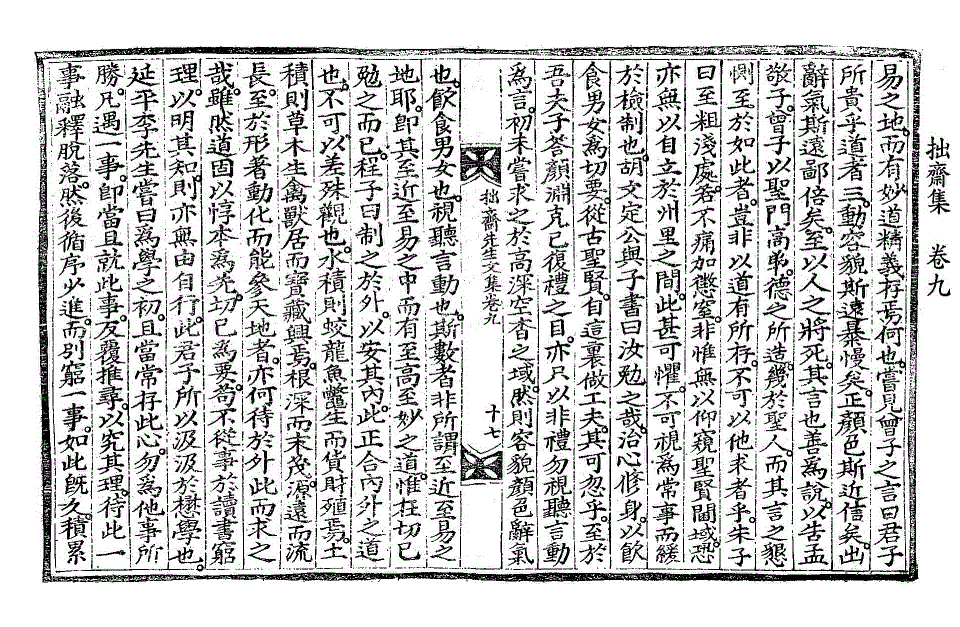 易之地。而有妙道精义存焉何也。尝见曾子之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至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说。以告孟敬子。曾子以圣门高弟。德之所造。几于圣人。而其言之恳恻至于如此者。岂非以道有所存。不可以他求者乎。朱子曰至粗浅处。若不痛加惩窒。非惟无以仰窥圣贤阃域。恐亦无以自立于州里之间。此甚可惧。不可视为常事而缓于检制也。胡文定公与子书曰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饮食男女为切要。从古圣贤。自这里做工夫。其可忽乎。至于吾夫子答颜渊克己复礼之目。亦只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为言。初未尝求之于高深空杳之域。然则容貌颜色辞气也。饮食男女也。视听言动也。斯数者非所谓至近至易之地耶。即其至近至易之中而有至高至妙之道。惟在切己勉之而已。程子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此正合内外之道也。不可以差殊观也。水积则蛟龙鱼鳖生而货财殖焉。土积则草木生禽兽居而宝藏兴焉。根深而末茂。源远而流长。至于形著动化而能参天地者。亦何待于外此而求之哉。虽然道固以惇本为先。切己为要。苟不从事于读书穷理。以明其知。则亦无由自行。此君子所以汲汲于懋学也。延平李先生尝曰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覆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
易之地。而有妙道精义存焉何也。尝见曾子之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至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说。以告孟敬子。曾子以圣门高弟。德之所造。几于圣人。而其言之恳恻至于如此者。岂非以道有所存。不可以他求者乎。朱子曰至粗浅处。若不痛加惩窒。非惟无以仰窥圣贤阃域。恐亦无以自立于州里之间。此甚可惧。不可视为常事而缓于检制也。胡文定公与子书曰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饮食男女为切要。从古圣贤。自这里做工夫。其可忽乎。至于吾夫子答颜渊克己复礼之目。亦只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为言。初未尝求之于高深空杳之域。然则容貌颜色辞气也。饮食男女也。视听言动也。斯数者非所谓至近至易之地耶。即其至近至易之中而有至高至妙之道。惟在切己勉之而已。程子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此正合内外之道也。不可以差殊观也。水积则蛟龙鱼鳖生而货财殖焉。土积则草木生禽兽居而宝藏兴焉。根深而末茂。源远而流长。至于形著动化而能参天地者。亦何待于外此而求之哉。虽然道固以惇本为先。切己为要。苟不从事于读书穷理。以明其知。则亦无由自行。此君子所以汲汲于懋学也。延平李先生尝曰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覆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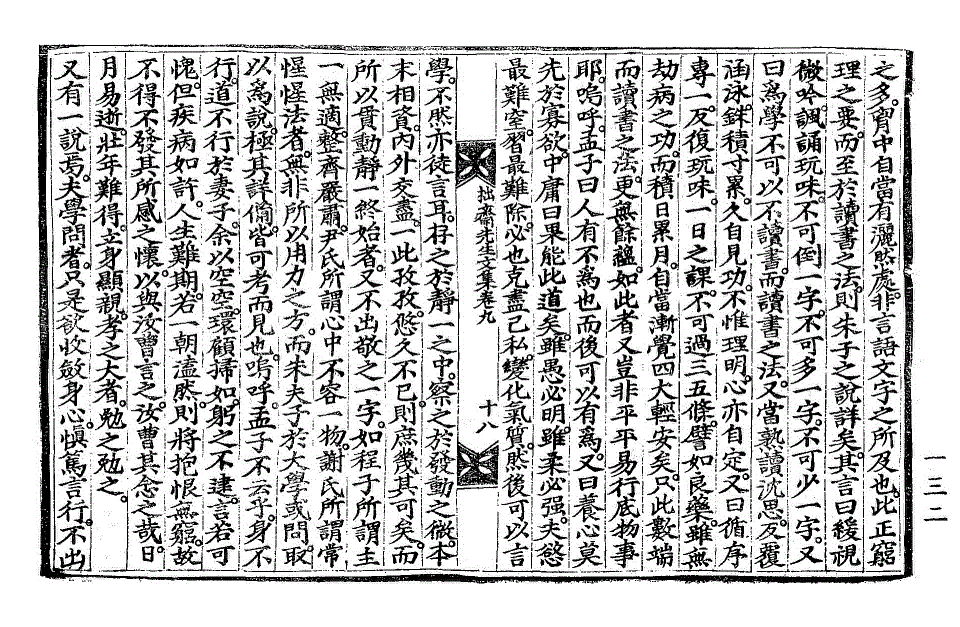 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言语文字之所及也。此正穷理之要。而至于读书之法。则朱子之说详矣。其言曰缓视微吟。讽诵玩味。不可倒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又曰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沈思。反覆涵泳。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又曰循序专一。反复玩味。一日之课。不可过三五条。譬如良药。虽无劫病之功。而积日累月。自当渐觉四大轻安矣。只此数端而读书之法。更无馀蕴。如此者又岂非平平易行底物事耶。呜呼。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又曰养心莫先于寡欲。中庸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夫欲最难窒。习最难除。必也克尽己私。变化气质。然后可以言学。不然亦徒言耳。存之于静一之中。察之于发动之微。本末相资。内外交尽。一此孜孜。悠久不已。则庶几其可矣。而所以贯动静一终始者。又不出敬之一字。如程子所谓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尹氏所谓心中不容一物。谢氏所谓常惺惺法者。无非所以用力之方。而朱夫子于大学或问。取以为说。极其详备。皆可考而见也。呜呼孟子不云乎。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余以空空。环顾扫如。躬之不逮。言若可愧。但疾病如许。人生难期。若一朝溘然。则将抱恨无穷。故不得不发其所感之怀。以与汝曹言之。汝曹其念之哉。日月易逝。壮年难得。立身显亲。孝之大者。勉之勉之。
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言语文字之所及也。此正穷理之要。而至于读书之法。则朱子之说详矣。其言曰缓视微吟。讽诵玩味。不可倒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又曰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沈思。反覆涵泳。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又曰循序专一。反复玩味。一日之课。不可过三五条。譬如良药。虽无劫病之功。而积日累月。自当渐觉四大轻安矣。只此数端而读书之法。更无馀蕴。如此者又岂非平平易行底物事耶。呜呼。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又曰养心莫先于寡欲。中庸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夫欲最难窒。习最难除。必也克尽己私。变化气质。然后可以言学。不然亦徒言耳。存之于静一之中。察之于发动之微。本末相资。内外交尽。一此孜孜。悠久不已。则庶几其可矣。而所以贯动静一终始者。又不出敬之一字。如程子所谓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尹氏所谓心中不容一物。谢氏所谓常惺惺法者。无非所以用力之方。而朱夫子于大学或问。取以为说。极其详备。皆可考而见也。呜呼孟子不云乎。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余以空空。环顾扫如。躬之不逮。言若可愧。但疾病如许。人生难期。若一朝溘然。则将抱恨无穷。故不得不发其所感之怀。以与汝曹言之。汝曹其念之哉。日月易逝。壮年难得。立身显亲。孝之大者。勉之勉之。又有一说焉。夫学问者。只是欲收敛身心。慎笃言行。不出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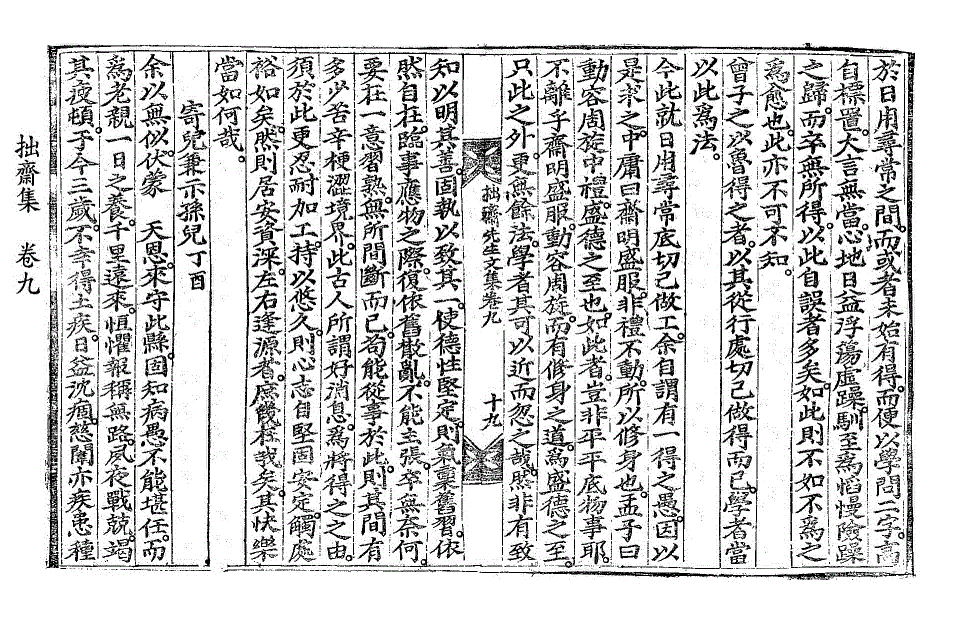 于日用寻常之间。而或者未始有得。而便以学问二字。高自标置。大言无当。心地日益浮荡虚躁。驯至为慆慢险躁之归。而卒无所得。以此自误者多矣。如此则不如不为之为愈也。此亦不可不知。
于日用寻常之间。而或者未始有得。而便以学问二字。高自标置。大言无当。心地日益浮荡虚躁。驯至为慆慢险躁之归。而卒无所得。以此自误者多矣。如此则不如不为之为愈也。此亦不可不知。曾子之以鲁得之者。以其从行处切己做得而已。学者当以此为法。
今此就日用寻常底切己做工。余自谓有一得之愚。因以是求之。中庸曰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如此者。岂非平平底物事耶。不离乎斋明盛服。动容周旋。而有修身之道。为盛德之至。只此之外。更无馀法。学者其可以近而忽之哉。然非有致知以明其善。固执以致其一。使德性坚定。则气禀旧习。依然自在。临事应物之际。复依旧散乱。不能主张。卒无奈何。要在一意习熟。无所间断而已。苟能从事于此。则其间有多少苦辛梗涩境界。此古人所谓好消息。为将得之之由。须于此更忍耐加工。持以悠久。则心志自坚固安定。触处裕如矣。然则居安资深。左右逢源者。庶几在我矣。其快乐当如何哉。
寄儿兼示孙儿(丁酉)
余以无似。伏蒙 天恩。来守此县。固知病愚不能堪任。而为老亲一日之养。千里远来。恒惧报称无路。夙夜战兢。竭其疲顿。于今三岁。不幸得土疾。日益沈痼。慈闱亦疾患种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3L 页
 种。白首他乡。情事可想。求退不得。闷默度日。今又添得伤寒。宿病转剧。元气看看益尽。恐不能起。而汝辈又在远不得相见。不为一言。因遂溘然。则将抱恨无穷。故拨昏书此。汝曹识之。我祖考府君遗训孔昭。临终时诗曰勉尔儿曹须慎旃。忠孝之外无事业。又遗戒曰力念善事。力行善事。每一奉读。不胜怆然。我先考孝友出天。至行在人耳目。不幸早世。终天之痛。为如何哉。余幼学于季父持平公。公每教之曰人以德行为本。苟无其本。虽文如锦绣何益。每以忠孝清白。毋失家传旧业为诫。谆谆不已。虽愚不能及。而常铭镂在心。不敢忘怠。耿耿若前日事。惟是禀气昏弱。随事弛废。不能自强。使汝曹无以观感。只自愧责何言。余尝念持身之道。在循循雅饬。谨慎不放。守拙安分。不求荣宦。不贪货利。不言人过失。不是非 朝家政法。不谈州县官员得失。不言边报差除。不传说灾异妖怪。居家则谨守家规。(考家礼序文可见)居官则谨守法度。不求人知。勿接异色人。(如巫卜相士凡杂术及市井牟利之人。见小学中。)不止居官者当然。人皆当谨畏。避权势。难进易退。亦无与有权势人交游。常爱马援诫兄子书。亦常爱马少游平生敛退卑让。不与人争校。退溪先生一生退让。屡徵不起。潜心于性理之学。德盛业广。令闻延世。我祖考出处行迹。亦略相似。虽非后学末裔所敢希望。立心则不可不如此。盖以圣贤为准的。纵不能及。犹可为善士。若立志不高。以中下自处。则终为下流之归而已。念
种。白首他乡。情事可想。求退不得。闷默度日。今又添得伤寒。宿病转剧。元气看看益尽。恐不能起。而汝辈又在远不得相见。不为一言。因遂溘然。则将抱恨无穷。故拨昏书此。汝曹识之。我祖考府君遗训孔昭。临终时诗曰勉尔儿曹须慎旃。忠孝之外无事业。又遗戒曰力念善事。力行善事。每一奉读。不胜怆然。我先考孝友出天。至行在人耳目。不幸早世。终天之痛。为如何哉。余幼学于季父持平公。公每教之曰人以德行为本。苟无其本。虽文如锦绣何益。每以忠孝清白。毋失家传旧业为诫。谆谆不已。虽愚不能及。而常铭镂在心。不敢忘怠。耿耿若前日事。惟是禀气昏弱。随事弛废。不能自强。使汝曹无以观感。只自愧责何言。余尝念持身之道。在循循雅饬。谨慎不放。守拙安分。不求荣宦。不贪货利。不言人过失。不是非 朝家政法。不谈州县官员得失。不言边报差除。不传说灾异妖怪。居家则谨守家规。(考家礼序文可见)居官则谨守法度。不求人知。勿接异色人。(如巫卜相士凡杂术及市井牟利之人。见小学中。)不止居官者当然。人皆当谨畏。避权势。难进易退。亦无与有权势人交游。常爱马援诫兄子书。亦常爱马少游平生敛退卑让。不与人争校。退溪先生一生退让。屡徵不起。潜心于性理之学。德盛业广。令闻延世。我祖考出处行迹。亦略相似。虽非后学末裔所敢希望。立心则不可不如此。盖以圣贤为准的。纵不能及。犹可为善士。若立志不高。以中下自处。则终为下流之归而已。念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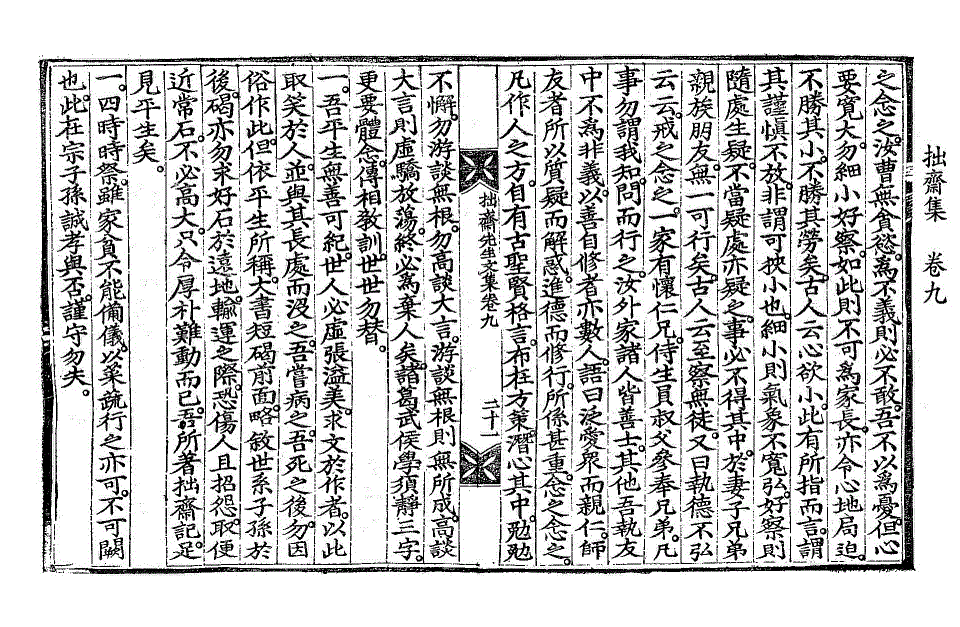 之念之。汝曹无贪欲。为不义则必不敢。吾不以为忧。但心要宽大。勿细小好察。如此则不可为家长。亦令心地局迫。不胜其小。不胜其劳矣。古人云心欲小。此有所指而言。谓其谨慎不放。非谓可狭小也。细小则气象不宽弘。好察则随处生疑。不当疑处亦疑之。事必不得其中。于妻子兄弟亲族朋友。无一可行矣。古人云至察无徒。又曰执德不弘云云。戒之念之。一家有怀仁兄。侍生员叔父参奉兄弟。凡事勿谓我知。问而行之。汝外家诸人皆善士。其他吾执友中不为非义。以善自修者亦数人。语曰泛爱众而亲仁。师友者所以质疑而解惑。进德而修行。所系甚重。念之念之。凡作人之方。自有古圣贤格言。布在方策。潜心其中。勉勉不懈。勿游谈无根。勿高谈大言。游谈无根则无所成。高谈大言则虚骄放荡。终必为弃人矣。诸葛武侯学须静三字。更要体念。传相教训。世世勿替。
之念之。汝曹无贪欲。为不义则必不敢。吾不以为忧。但心要宽大。勿细小好察。如此则不可为家长。亦令心地局迫。不胜其小。不胜其劳矣。古人云心欲小。此有所指而言。谓其谨慎不放。非谓可狭小也。细小则气象不宽弘。好察则随处生疑。不当疑处亦疑之。事必不得其中。于妻子兄弟亲族朋友。无一可行矣。古人云至察无徒。又曰执德不弘云云。戒之念之。一家有怀仁兄。侍生员叔父参奉兄弟。凡事勿谓我知。问而行之。汝外家诸人皆善士。其他吾执友中不为非义。以善自修者亦数人。语曰泛爱众而亲仁。师友者所以质疑而解惑。进德而修行。所系甚重。念之念之。凡作人之方。自有古圣贤格言。布在方策。潜心其中。勉勉不懈。勿游谈无根。勿高谈大言。游谈无根则无所成。高谈大言则虚骄放荡。终必为弃人矣。诸葛武侯学须静三字。更要体念。传相教训。世世勿替。一。吾平生无善可纪。世人必虚张溢美。求文于作者。以此取笑于人。并与其长处而没之。吾尝病之。吾死之后。勿因俗作此。但依平生所称。大书短碣前面。略叙世系子孙于后。碣亦勿求好石于远地。输运之际。恐伤人且招怨。取便近常石。不必高大。只令厚朴难动而已。吾所著拙斋记。足见平生矣。
一。四时时祭。虽家贫不能备仪。以菜蔬行之亦可。不可阙也。此在宗子孙诚孝与否。谨守勿失。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4L 页
 一。宗子孙有放荡不能守家规者。诸子孙共训戒之。谆谆恳恳。以感其心。期于有改。其贫乏不能自存者。则子孙中收合米谷以周之。勿令失所。
一。宗子孙有放荡不能守家规者。诸子孙共训戒之。谆谆恳恳。以感其心。期于有改。其贫乏不能自存者。则子孙中收合米谷以周之。勿令失所。一。子孙等。每以德义相训。有过失则相规。勿相争校失和气。凡亲族务相敦睦。邻里亦然。诗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此最致念致力处。
一。毋杂交游。毋妄言。此吾曾祖妣戒吾祖考府君语也。尔等宜刻骨。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谨之又谨。
我家无他物。惟忠孝清白。虽愚不能及。铭镂恒在骨。汝曹勤念此。须知我心曲。一豪(一作毫)苟自欺。神明在我侧。
寄宜河书(甲辰○在安奇)
汝上去后。绝不闻消息。郁郁。未知寓居何洞。无事供仕否。京中不比乡曲。处身极难。不可不慎。惟职事恪勤外。不可作閒杂说话。以触时讳。至于朝廷间是非及人物长短。尤不可妄议论。慎之慎之。吾亦仅支而衰败已甚。触事又多难堪。欲决归而姑未果耳。
寄答宜河书
见书知无事为慰。祭物之不得备具。势之所然奈何。前书所言事。吾非为督过于汝。平日每以汝有好察多疑之病。心常为汝忧之故言之。盖此病根不去而在。则随时随事。心境缴绕。不能和平。末梢必有不可说之事。且汝之病。于人之过。一以为然。则不曾更思。硬定把捉。终不放下。或有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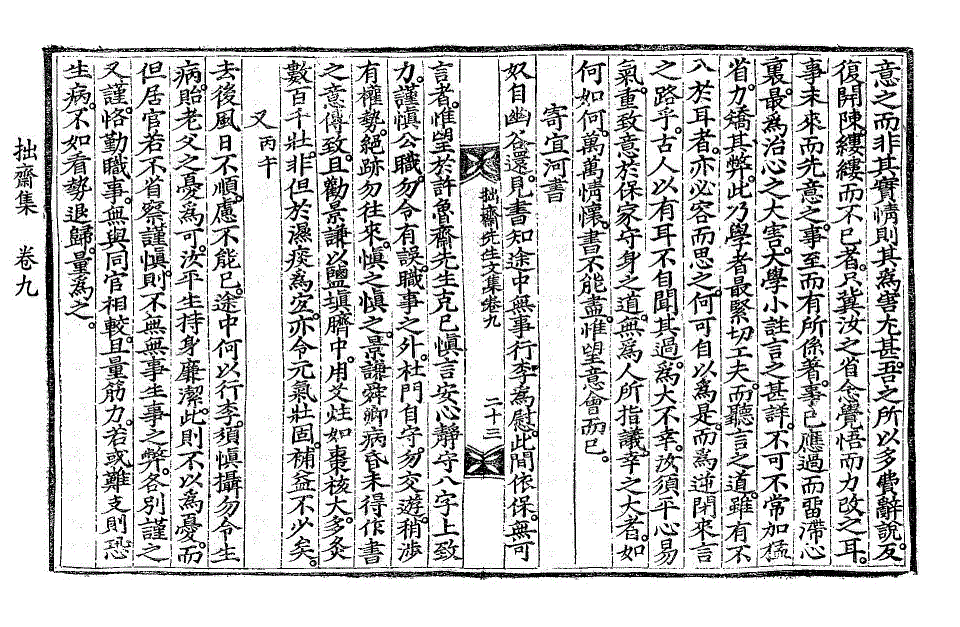 意之而非其实情则其为害尤甚。吾之所以多费辞说。反复开陈缕缕而不已者。只冀汝之省念觉悟而力改之耳。事未来而先意之。事至而有所系著。事已应过而留滞心里。最为治心之大害。大学小注言之甚详。不可不常加猛省。力矫其弊。此乃学者最紧切工夫。而听言之道。虽有不入于耳者。亦必容而思之。何可自以为是。而为逆闭来言之路乎。古人以有耳不自闻其过。为大不幸。汝须平心易气。重致意于保家守身之道。无为人所指议。幸之大者。如何如何。万万情怀。书不能尽。惟望意会而已。
意之而非其实情则其为害尤甚。吾之所以多费辞说。反复开陈缕缕而不已者。只冀汝之省念觉悟而力改之耳。事未来而先意之。事至而有所系著。事已应过而留滞心里。最为治心之大害。大学小注言之甚详。不可不常加猛省。力矫其弊。此乃学者最紧切工夫。而听言之道。虽有不入于耳者。亦必容而思之。何可自以为是。而为逆闭来言之路乎。古人以有耳不自闻其过。为大不幸。汝须平心易气。重致意于保家守身之道。无为人所指议。幸之大者。如何如何。万万情怀。书不能尽。惟望意会而已。寄宜河书
奴自幽谷还。见书知途中无事行李为慰。此间依保。无可言者。惟望于许鲁斋先生克己慎言安心静守八字上致力。谨慎公职。勿令有误。职事之外。杜门自守。勿交游。稍涉有权势。绝迹勿往来。慎之慎之。景谦舜卿病昏未得作书之意传致。且劝景谦以盐填脐中。用艾炷如枣核大。多灸数百千壮。非但于湿痰为宜。亦令元气壮固。补益不少矣。
寄宜河书(内午)
去后风日不顺。虑不能已。途中何以行李。须慎摄勿令生病。贻老父之忧为可。汝平生持身廉洁。此则不以为忧。而但居官若不省察谨慎。则不无无事生事之弊。各别谨之又谨。恪勤职事。无与同官相较。且量筋力。若或难支则恐生病。不如看势退归。量为之。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5L 页
 答宜河别纸(辛亥)
答宜河别纸(辛亥)唐柳玭语其子弟曰门地高。可畏而不可恃。虽有善人。不省录。少有差失则人必指而议之。必力行善事。仅可比凡常人。此其可畏而不可恃也。廉洁汝素自有。吾不须为汝言。但恐于无心中有未察处耳。孟子云不得罪于巨室。非谓其曲循巨室之意。为违道干誉事也。惟处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而已。慎之慎之。
闻客挠甚。逐日应接纷沓。则令心地荒乱。未遑料理官事。最为大害。须以此意。通于亲切人处。简其出入。况 国法有暗行囚禁私客状 启之事。尤不可令彼此俱得罪矣。以此通谕。姑为谢绝。有何不可乎。君则在其处。凡有阙失。请其随闻相告则为益必不少矣。季父公曾莅此邑。遗爱在民。更须谨慎。毋忝家声。
凡出一令作一事。必细思之。有可以致后弊者则一切勿为可也。古人云作一事。不如减一事。兴一利。不如去一害。又云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又云治邑如烹鲜。勿挠为上。此语皆可念也。程夫子云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又答刘安礼御吏之问曰。正己而格物。又答为治曰。使民各得输其情。此虽非凡人所敢望。然以此为心则虽不中不远矣。
古人云爱民如子。御吏如奴。此视民视吏之差。而束吏宽民。此其格式也。通下情最为切务。民则虽有不识体面而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6H 页
 失礼于眼前者。略之可也。官家下人与衙奴。自有相与体貌。衙奴之有汎滥者则固不可不禁。而下人如有蔑视衙奴而侮慢之。亦非所以敬谨事官员之道。不可不稍加诃禁。念之念之。
失礼于眼前者。略之可也。官家下人与衙奴。自有相与体貌。衙奴之有汎滥者则固不可不禁。而下人如有蔑视衙奴而侮慢之。亦非所以敬谨事官员之道。不可不稍加诃禁。念之念之。凡临下之道。以严为主而以宽济之然后为可。若以宽济宽。使下人生慢易之心。则大不可。闻汝以凶荒之故。凡下人之无礼者。不为纠检云然耶。更须摄之。
如或有本家奴子作弊于境内者。则不可不严禁。须挂榜知委于境内。如有如此之事。令即驱逐。使不得接迹于境内。至于兴贩买卖于境内场市者。尤为痛禁。
衙内不严则必惹起人言。须戒敕。使内言不出于外。外言不入于内。如有以外间事告语者。问其言根之所自来而痛治其罪。惟下人以公事。因奴子告课者不禁。奴婢切不许出衙门外往场市。官婢亦不令得入衙内。而官巫女亦禁绝之可也。曾见居官者。防禁不严。或有下人因缘纳膳物衙属及奴婢者。流寓女人入谒衙属者。凡致官员受贿赂之谤者多以此。切须禁之。小学有当官者禁绝异色人之语。皆不可不察也。凡干请嘱事。一切勿施。若一开路则必不胜其纷纷矣。
乡所之言。虽不可不听。亦不可一一准信。若不致察则必有见欺误事之弊矣。
凡饥民必令纳其户口而考准。亦防奸之一事也。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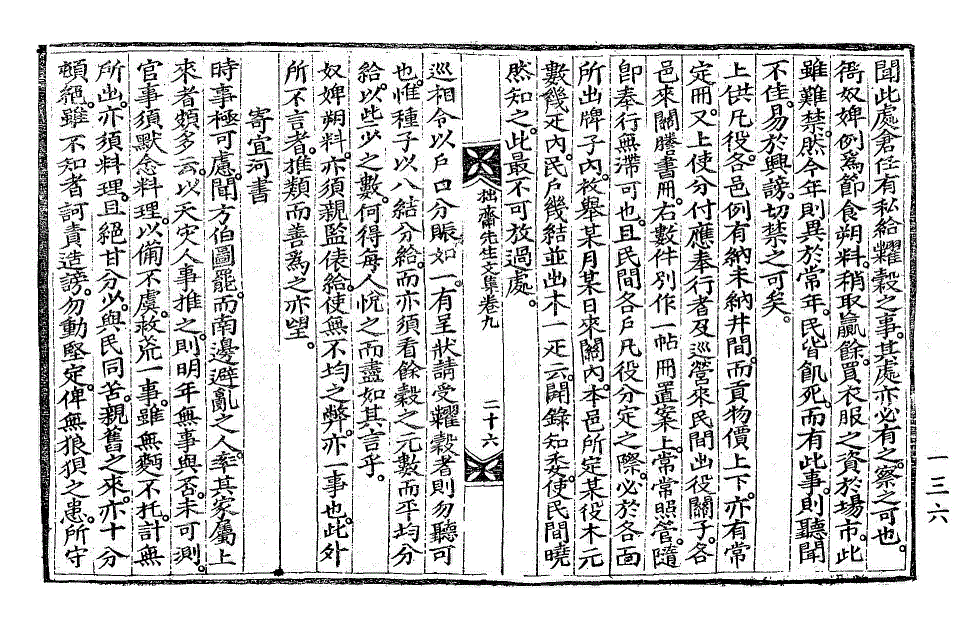 闻此处仓任有私给粜谷之事。其处亦必有之。察之可也。
闻此处仓任有私给粜谷之事。其处亦必有之。察之可也。衙奴婢例为节食朔料。稍取赢馀。买衣服之资于场市。此虽难禁。然今年则异于常年。民皆饥死而有此事。则听闻不佳。易于兴谤。切禁之可矣。
上供凡役。各邑例有纳未纳井间。而贡物价上下。亦有常定册。又上使分付应奉行者及巡营来民间出役关子。各邑来关誊书册。右数件别作一帖册置案上。常常照管。随即奉行无滞可也。且民间各户凡役分定之际。必于各面所出牌子内。枚举某月某日来关内。本邑所定某役木元数几疋内。民户几结并出木一疋云。开录知委。使民间晓然知之。此最不可放过处。
巡相令以户口分赈如一。有呈状请受粜谷者则勿听可也。惟种子以八结分给。而亦须看馀谷之元数而平均分给。以些少之数。何得每人悦之而尽如其言乎。
奴婢朔料。亦须亲监俵给。使无不均之弊。亦一事也。此外所不言者。推类而善为之亦望。
寄宜河书
时事极可虑。闻方伯图罢。而南边避乱之人。率其家属上来者颇多云。以天灾人事推之。则明年无事与否。未可测官事须默念料理。以备不虞。救荒一事。虽无面不托。计无所出。亦须料理。且绝甘分少。与民同苦。亲旧之来。亦十分顿绝。虽不知者诃责造谤。勿动坚定。俾无狼狈之患。所守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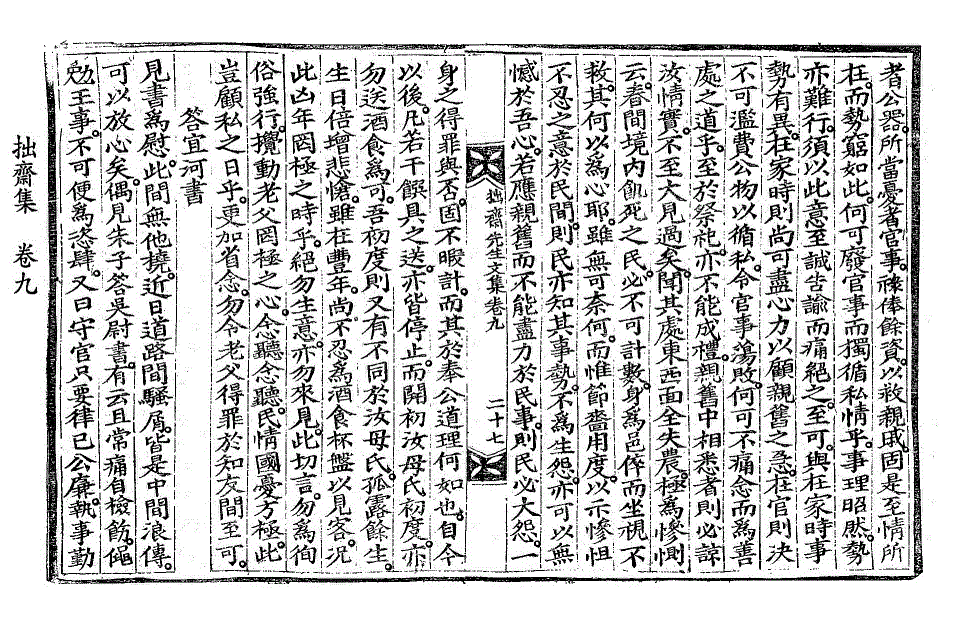 者公器。所当忧者官事。禄俸馀资。以救亲戚。固是至情所在。而势穷如此。何可废官事而独循私情乎。事理昭然势亦难行。须以此意至诚告谕而痛绝之。至可。与在家时事势有异。在家时则尚可尽心力以顾亲旧之急。在官则决不可滥费公物以循私。令官事荡败。何可不痛念而为善处之道乎。至于祭祀。亦不能成礼。亲旧中相悉者则必谅汝情实。不至大见过矣。闻其处东西面全失农。极为惨恻云。春间境内饥死之民。必不可计数。身为邑倅而坐视不救。其何以为心耶。虽无可奈何。而惟节啬用度。以示惨怚不忍之意于民间。则民亦知其事势。不为生怨。亦可以无憾于吾心。若应亲旧而不能尽力于民事。则民必大怨。一身之得罪与否。固不暇计。而其于奉公道理何如也。自今以后。凡若干馔具之送。亦皆停止。而开初汝母氏初度。亦勿送酒食为可。吾初度则又有不同于汝母氏。孤露馀生。生日倍增悲怆。虽在丰年。尚不忍为酒食杯盘以见客。况此凶年罔极之时乎。绝勿生意。亦勿来见。此切言。勿为徇俗强行。搅动老父罔极之心。念听念听。民情国忧方极。此岂顾私之日乎。更加省念。勿令老父得罪于知友间至可。
者公器。所当忧者官事。禄俸馀资。以救亲戚。固是至情所在。而势穷如此。何可废官事而独循私情乎。事理昭然势亦难行。须以此意至诚告谕而痛绝之。至可。与在家时事势有异。在家时则尚可尽心力以顾亲旧之急。在官则决不可滥费公物以循私。令官事荡败。何可不痛念而为善处之道乎。至于祭祀。亦不能成礼。亲旧中相悉者则必谅汝情实。不至大见过矣。闻其处东西面全失农。极为惨恻云。春间境内饥死之民。必不可计数。身为邑倅而坐视不救。其何以为心耶。虽无可奈何。而惟节啬用度。以示惨怚不忍之意于民间。则民亦知其事势。不为生怨。亦可以无憾于吾心。若应亲旧而不能尽力于民事。则民必大怨。一身之得罪与否。固不暇计。而其于奉公道理何如也。自今以后。凡若干馔具之送。亦皆停止。而开初汝母氏初度。亦勿送酒食为可。吾初度则又有不同于汝母氏。孤露馀生。生日倍增悲怆。虽在丰年。尚不忍为酒食杯盘以见客。况此凶年罔极之时乎。绝勿生意。亦勿来见。此切言。勿为徇俗强行。搅动老父罔极之心。念听念听。民情国忧方极。此岂顾私之日乎。更加省念。勿令老父得罪于知友间至可。答宜河书
见书为慰。此间无他挠。近日道路间骚屑。皆是中间浪传。可以放心矣。偶见朱子答吴尉书。有云且常痛自检饬。僶勉王事。不可便为恣肆。又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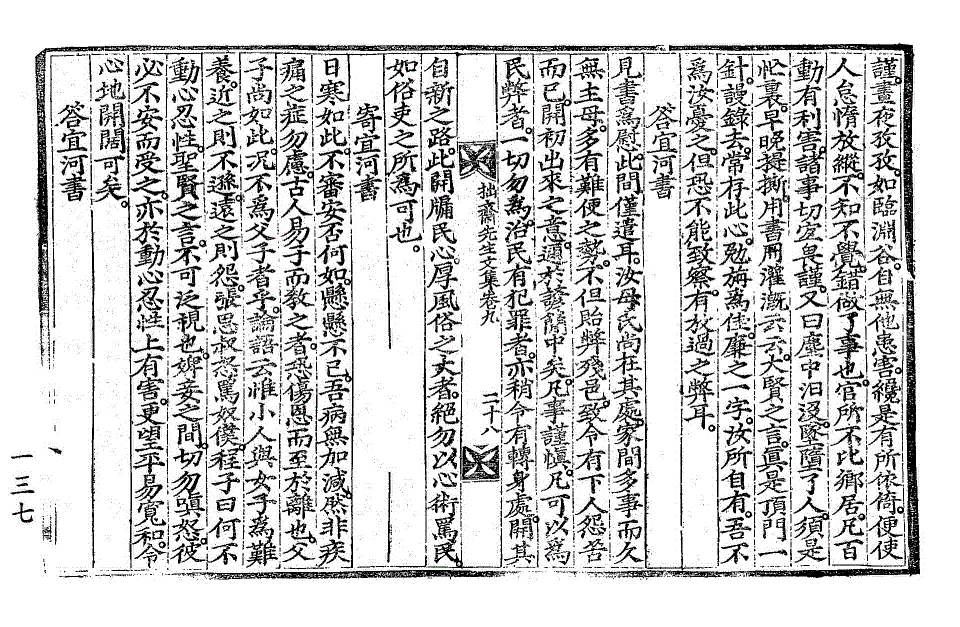 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自无他患害。才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错做了事也。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又曰尘中汩没。坠堕了人。须是忙里。早晚提撕。用书册灌溉云云。大贤之言。真是顶门一针。谩录去。常存此心。勉旃为佳。廉之一字。汝所自有。吾不为汝忧之。但恐不能致察。有放过之弊耳。
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自无他患害。才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错做了事也。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又曰尘中汩没。坠堕了人。须是忙里。早晚提撕。用书册灌溉云云。大贤之言。真是顶门一针。谩录去。常存此心。勉旃为佳。廉之一字。汝所自有。吾不为汝忧之。但恐不能致察。有放过之弊耳。答宜河书
见书为慰。此间仅遣耳。汝母氏尚在其处。家间多事而久无主母。多有难便之势。不但贻弊残邑。致令有下人怨苦而已。开初出来之意。迩于谚𥳑中矣。凡事谨慎。凡可以为民弊者。一切勿为。治民有犯罪者。亦稍令有转身处。开其自新之路。此开牖民心。厚风俗之大者。绝勿以心术骂民。如俗吏之所为可也。
寄宜河书
日寒如此。不审安否何如。悬悬不已。吾病无加减。然非疾痛之症勿虑。古人易子而教之者。恐伤恩而至于离也。父子尚如此。况不为父子者乎。论语云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张思叔怒骂奴仆。程子曰何不动心忍性。圣贤之言。不可泛视也。婢妾之间。切勿嗔怒。彼必不安而受之。亦于动心忍性上有害。更望平易宽和。令心地开阔可矣。
答宜河书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8H 页
 奴还见书为慰。吾病非偶然所发。若非针药治疗。何能得速效也。闻汝来月欲出来云。此甚不便。吾病如此。不得出门见客。汝之从外接客。甚非所以来之意。且生朝倍增悲怆。是程子说。况老境怀抱。尤为难忍。更有何心安受汝所享之杯盘乎。此又不可之大者。徒为观美而违老父之意。亦非养志之事。须千万勿为出来。至可至可。来则必增病中烦恼。勿来勿来。
奴还见书为慰。吾病非偶然所发。若非针药治疗。何能得速效也。闻汝来月欲出来云。此甚不便。吾病如此。不得出门见客。汝之从外接客。甚非所以来之意。且生朝倍增悲怆。是程子说。况老境怀抱。尤为难忍。更有何心安受汝所享之杯盘乎。此又不可之大者。徒为观美而违老父之意。亦非养志之事。须千万勿为出来。至可至可。来则必增病中烦恼。勿来勿来。寄宜河别纸
近观旅轩先生集。得两言甚好。故并以示之。其一曰以宁静宽和。为养心持身之本。而又必察于义理之精。以谦恭忠信。为待人接物之道。而又不失正直之守。其二曰人间万福。莫最平安二字。所谓平安者。心平身平家平族平也。心与身与家与族。既得其平。则安在其中矣。只愿更求其所以平者。反身而笃之云云。此言甚好。吾以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心平气和则祥必应之。万福皆由此致之。反是则气之所乖。灾必生焉。所谓宽而居之。容而思之也。和则事事皆顺。物无不和也。苟能常存此心。久而得力。则心地开阔。无时不乐。其平可知。此非但福之所由生。亦可以得养寿命之效。岂不乐哉。更望致力为妙。
大学语孟中庸常循环玩绎。于治心养性应事接物。得力必深。不须奔程趁限。如经生课诵以应科试。但能无贪多无欲速。勿规近效。勿作辍。玩而复之。熟读详味。久后自能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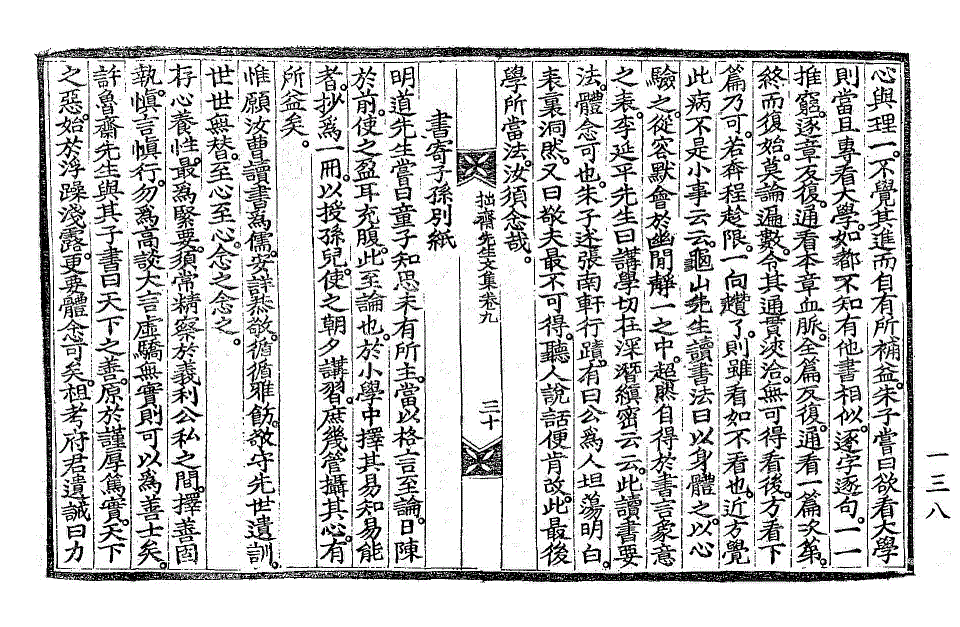 心与理一。不觉其进而自有所补益。朱子尝曰欲看大学则当且专看大学。如都不知有他书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穷。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莫论遍数。令其通贯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下篇乃可。若奔程趁限。一向趱了。则虽看如不看也。近方觉此病不是小事云云。龟山先生读书法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李延平先生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云云。此读书要法。体念可也。朱子述张南轩行迹。有曰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又曰敬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此最后学所当法。汝须念哉。
心与理一。不觉其进而自有所补益。朱子尝曰欲看大学则当且专看大学。如都不知有他书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穷。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莫论遍数。令其通贯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下篇乃可。若奔程趁限。一向趱了。则虽看如不看也。近方觉此病不是小事云云。龟山先生读书法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李延平先生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云云。此读书要法。体念可也。朱子述张南轩行迹。有曰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又曰敬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此最后学所当法。汝须念哉。书寄子孙别纸
明道先生尝曰童子知思未有所主。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使之盈耳充腹。此至论也。于小学中择其易知易能者。抄为一册。以授孙儿。使之朝夕讲习。庶几管摄其心。有所益矣。
惟愿汝曹读书为儒。安详恭敬。循循雅饬。敬守先世遗训。世世无替。至心至心。念之念之。
存心养性。最为紧要。须常精察于义利公私之间。择善固执。慎言慎行。勿为高谈大言虚骄无实则可以为善士矣。许鲁斋先生与其子书曰天下之善。原于谨厚笃实。天下之恶。始于浮躁浅露。更要体念可矣。祖考府君遗诫曰力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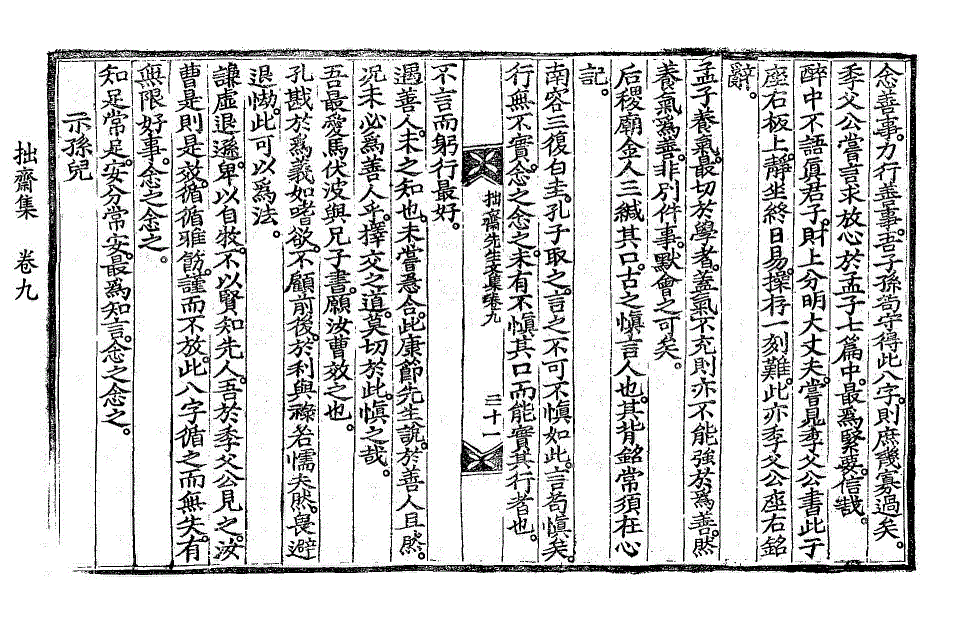 念善事。力行善事。吾子孙苟守得此八字。则庶几寡过矣。
念善事。力行善事。吾子孙苟守得此八字。则庶几寡过矣。季父公尝言求放心于孟子七篇中。最为紧要。信哉。
醉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尝见季父公书此于座右板上。静坐终日易。操存一刻难。此亦季父公座右铭辞。
孟子养气。最切于学者。盖气不充则亦不能强于为善。然养气为善。非别件事。默会之可矣。
后稷庙金人三缄其口。古之慎言人也。其背铭常须在心记。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取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言苟慎矣。行无不实。念之念之。未有不慎其口而能实其行者也。
不言而躬行最好。
遇善人。未之知也。未尝急合。此康节先生说。于善人且然。况未必为善人乎。择交之道。莫切于此。慎之哉。
吾最爱马伏波与兄子书。愿汝曹效之也。
孔戡于为义如嗜欲。不顾前后。于利与禄若懦夫然。畏避退㤼。此可以为法。
谦虚退逊。卑以自牧。不以贤知先人。吾于季父公见之。汝曹是则是效。循循雅饬。谨而不放。此八字循之而无失。有无限好事。念之念之。
知足常足。安分常安。最为知言。念之念之。
示孙儿
拙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139L 页
 士之读书。将以穷理尽性。以善其身。古圣人教人作人之方。俱在方策。惟日孜孜。勉而至之。若但措心于记诵词章之间。又其下者。求利禄名声。抑亦末矣。季父公尝教我曰士以德行为先。苟为不然。虽文如锦绣奚益。此实切至之言。书与孙儿。汝曹识之。循循雅饬。谨言不放。虽未及圣贤。亦不失为善士。昔刘元城受不妄语三字于涑水先生。力行七年。表里如一。又马伏波遗兄子书。不啻恳至。念之念之。
士之读书。将以穷理尽性。以善其身。古圣人教人作人之方。俱在方策。惟日孜孜。勉而至之。若但措心于记诵词章之间。又其下者。求利禄名声。抑亦末矣。季父公尝教我曰士以德行为先。苟为不然。虽文如锦绣奚益。此实切至之言。书与孙儿。汝曹识之。循循雅饬。谨言不放。虽未及圣贤。亦不失为善士。昔刘元城受不妄语三字于涑水先生。力行七年。表里如一。又马伏波遗兄子书。不啻恳至。念之念之。示孙儿
退溪先生与人书。有曰贤关。有孟门之险。余以为宦路亦然。须一向退步。勿贪荣宦。稍涉有势利人。切勿与交游。畏避谨慎可矣。老先生一生谦退。养德山林。凡其所有高官大爵。皆在家时所受得者。考诸年谱及集中辞免文字可知。可以为法。士须以保全令名。毋坠家声为心。书与孙儿识之。更愿省念。勿以我言耄而忽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