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献议
献议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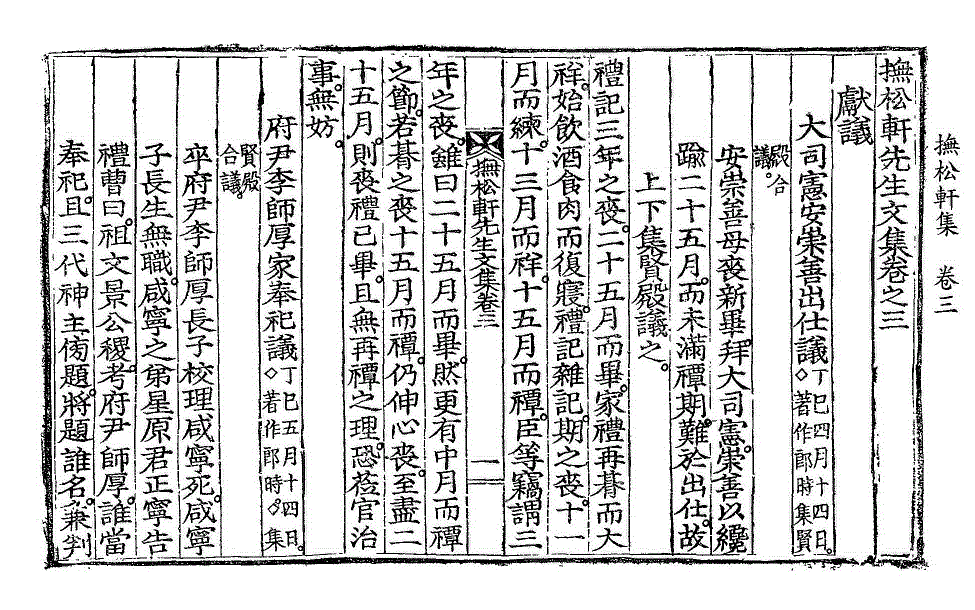 大司宪安崇善出仕议(丁巳四月十四日。○著作郎时。○集贤殿合议。)
大司宪安崇善出仕议(丁巳四月十四日。○著作郎时。○集贤殿合议。)安崇善母丧新毕。拜大司宪。崇善以才踰二十五月。而未满禫期。难于出仕。故 上下集贤殿议之。
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家礼再期而大祥。始饮酒食肉而复寝。礼记杂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臣等窃谓三年之丧。虽曰二十五月而毕。然更有中月而禫之节。若期之丧十五月而禫。仍伸心丧。至尽二十五月。则丧礼已毕。且无再禫之理。恐莅官治事。无妨。
府尹李师厚家奉祀议(丁巳五月十四日。○著作郎时。○集贤殿合议。)
卒府尹李师厚长子校理咸宁死。咸宁子长生无职。咸宁之弟星原君正宁告礼曹曰。祖文景公稷。考府尹师厚。谁当奉祀。且三代神主傍题。将题谁名。兼判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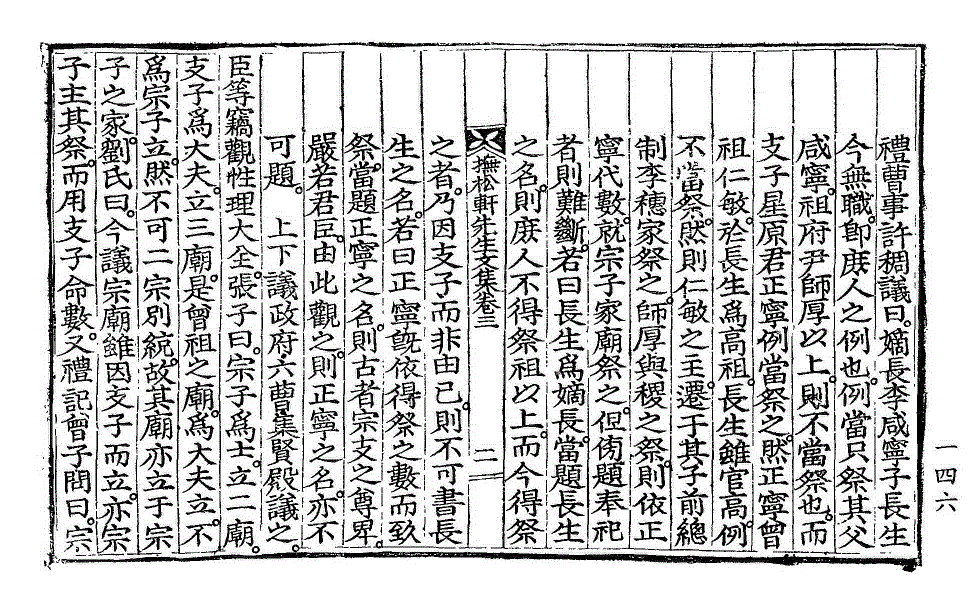 礼曹事许稠议曰。嫡长李咸宁子长生今无职。即庶人之例也。例当只祭其父咸宁。祖府尹师厚以上。则不当祭也。而支子星原君正宁例当祭之。然正宁曾祖仁敏。于长生为高祖。长生虽官高。例不当祭。然则仁敏之主。迁于其子前总制李穗家祭之。师厚与稷之祭。则依正宁代数。就宗子家庙祭之。但傍题奉祀者则难断。若曰长生为嫡长。当题长生之名。则庶人不得祭祖以上。而今得祭之者。乃因支子而非由己。则不可书长生之名。若曰正宁既依得祭之数而致祭。当题正宁之名。则古者宗支之尊卑。严若君臣。由此观之。则正宁之名。亦不可题。 上下议政府,六曹,集贤殿议之。
礼曹事许稠议曰。嫡长李咸宁子长生今无职。即庶人之例也。例当只祭其父咸宁。祖府尹师厚以上。则不当祭也。而支子星原君正宁例当祭之。然正宁曾祖仁敏。于长生为高祖。长生虽官高。例不当祭。然则仁敏之主。迁于其子前总制李穗家祭之。师厚与稷之祭。则依正宁代数。就宗子家庙祭之。但傍题奉祀者则难断。若曰长生为嫡长。当题长生之名。则庶人不得祭祖以上。而今得祭之者。乃因支子而非由己。则不可书长生之名。若曰正宁既依得祭之数而致祭。当题正宁之名。则古者宗支之尊卑。严若君臣。由此观之。则正宁之名。亦不可题。 上下议政府,六曹,集贤殿议之。臣等窃观性理大全。张子曰。宗子为士。立二庙。支子为大夫。立三庙。是曾祖之庙。为大夫立。不为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别统。故其庙亦立于宗子之家。刘氏曰。今议宗庙虽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支子命数。又礼记曾子问曰。宗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7H 页
 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以此观之。宗子为士。支子为大夫。则礼当立其三庙。而宗子以支子之命数。主其祭矣。既曰主祭。则安有傍题支子之理乎。而况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是支子于庙。虽用己之命数。然必因宗子而行其礼矣。是不当题支子之名矣。且性理大全注高氏曰。观木主之制。傍题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废。宗子承家主祀。有君之道。故诸子不得而抗焉。然则岂可以一时职秩之高下。夺宗而傍题支子之名。以乱万世宗支之分哉。请依河演议。令长生主祭。或曰。师厚神主。宜若于长生家庙祭之。然师元,师纯。皆师厚之弟。于咸宁叔父也。献酌之际。于师厚则以弟献兄可也。于咸宁则以叔献侄。不可也。曾子问。宗子死。称名不言孝。身殁而已。吕大均注曰。宗子死。庶子尚在。若有宗子之嫡子。未得主祭。故庶子主之。遂谓稷之神主。师元主之。师厚神主。正宁主之。定议以闻。令礼曹立法。
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以此观之。宗子为士。支子为大夫。则礼当立其三庙。而宗子以支子之命数。主其祭矣。既曰主祭。则安有傍题支子之理乎。而况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是支子于庙。虽用己之命数。然必因宗子而行其礼矣。是不当题支子之名矣。且性理大全注高氏曰。观木主之制。傍题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废。宗子承家主祀。有君之道。故诸子不得而抗焉。然则岂可以一时职秩之高下。夺宗而傍题支子之名。以乱万世宗支之分哉。请依河演议。令长生主祭。或曰。师厚神主。宜若于长生家庙祭之。然师元,师纯。皆师厚之弟。于咸宁叔父也。献酌之际。于师厚则以弟献兄可也。于咸宁则以叔献侄。不可也。曾子问。宗子死。称名不言孝。身殁而已。吕大均注曰。宗子死。庶子尚在。若有宗子之嫡子。未得主祭。故庶子主之。遂谓稷之神主。师元主之。师厚神主。正宁主之。定议以闻。令礼曹立法。附礼曹判书河演议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7L 页
 长生今虽幼弱无职。支子正宁依古制及六典。就宗子家庙。得祭三代。仁敏之主。代尽当出。就其子前总制李穗家祭之。神主傍题。则宗子长生例当题名。然当丧未毕。如家礼大祥改题主仪。待其丧毕。书长生之名。何如。
长生今虽幼弱无职。支子正宁依古制及六典。就宗子家庙。得祭三代。仁敏之主。代尽当出。就其子前总制李穗家祭之。神主傍题。则宗子长生例当题名。然当丧未毕。如家礼大祥改题主仪。待其丧毕。书长生之名。何如。附权蹈议
或者所引曾子问之辞。宗子去在他国而死者其祭如是。非谓其经常之法也。公仪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子游问诸孔子。子曰。否。立孙。此经常不易之礼也。孔子辨明之礼如是。而不复考。惑于吕氏之说。欲立万世经常之法。不亦谬乎。又按文公家礼祠堂图。诸父诸兄位。皆在主人之前。又于四时祭云初献主人。亚献主妇。终献兄弟之长。或长男或亲朋为之。无伯叔诸父献酌之文。不此之顾。乃有此论。请依集贤殿及河演议。仁敏神主。依礼就李穗家祭之。其稷以下三代。令长生立庙。而书长生奉祀。师元以下。皆以诸父与祭。无献酌之礼。乞以此为制。
继祖母服议(丁巳五月十八日。○著作郎时。○集贤殿合议。)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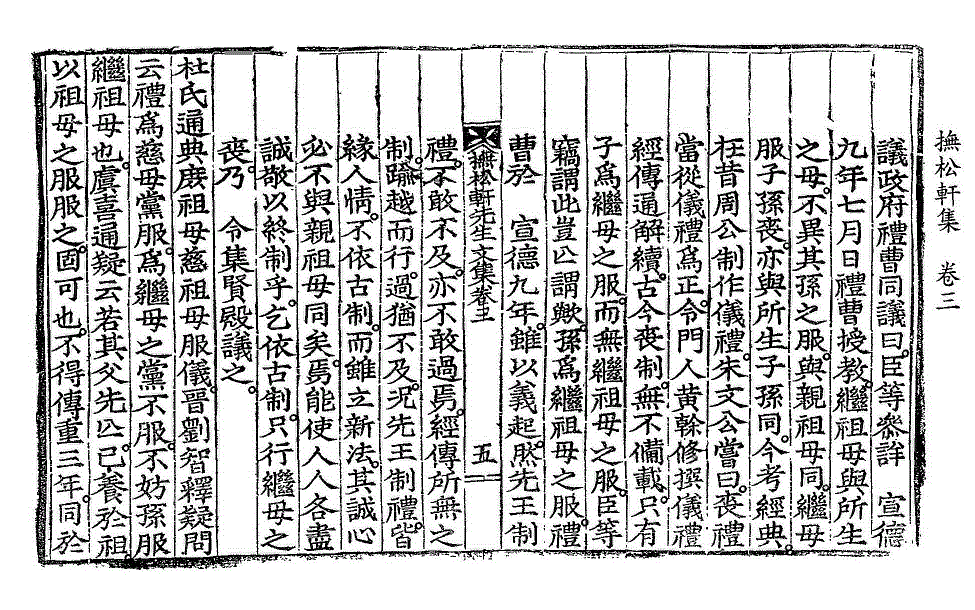 议政府礼曹同议曰。臣等参详 宣德九年七月日礼曹授教。继祖母与所生之母。不异其孙之服。与亲祖母同。继母服子孙丧。亦与所生子孙同。今考经典。在昔周公制作仪礼。朱文公尝曰。丧礼当从仪礼为正。令门人黄干修撰仪礼经传通解续。古今丧制。无不备载。只有子为继母之服。而无继祖母之服。臣等窃谓此岂亡谓欤。孙为继祖母之服。礼曹于 宣德九年。虽以义起。然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亦不敢过焉。经传所无之制。踰越而行。过犹不及。况先王制礼。皆缘人情。不依古制。而虽立新法。其诚心必不与亲祖母同矣。焉能使人人各尽诚敬以终制乎。乞依古制。只行继母之丧。乃 令集贤殿议之。
议政府礼曹同议曰。臣等参详 宣德九年七月日礼曹授教。继祖母与所生之母。不异其孙之服。与亲祖母同。继母服子孙丧。亦与所生子孙同。今考经典。在昔周公制作仪礼。朱文公尝曰。丧礼当从仪礼为正。令门人黄干修撰仪礼经传通解续。古今丧制。无不备载。只有子为继母之服。而无继祖母之服。臣等窃谓此岂亡谓欤。孙为继祖母之服。礼曹于 宣德九年。虽以义起。然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亦不敢过焉。经传所无之制。踰越而行。过犹不及。况先王制礼。皆缘人情。不依古制。而虽立新法。其诚心必不与亲祖母同矣。焉能使人人各尽诚敬以终制乎。乞依古制。只行继母之丧。乃 令集贤殿议之。杜氏通典庶祖母慈祖母服仪。晋刘智释疑问云礼为慈母党服。为继母之党不服。不妨孙服继祖母也。虞喜通疑云若其父先亡。己养于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固可也。不得传重三年。同于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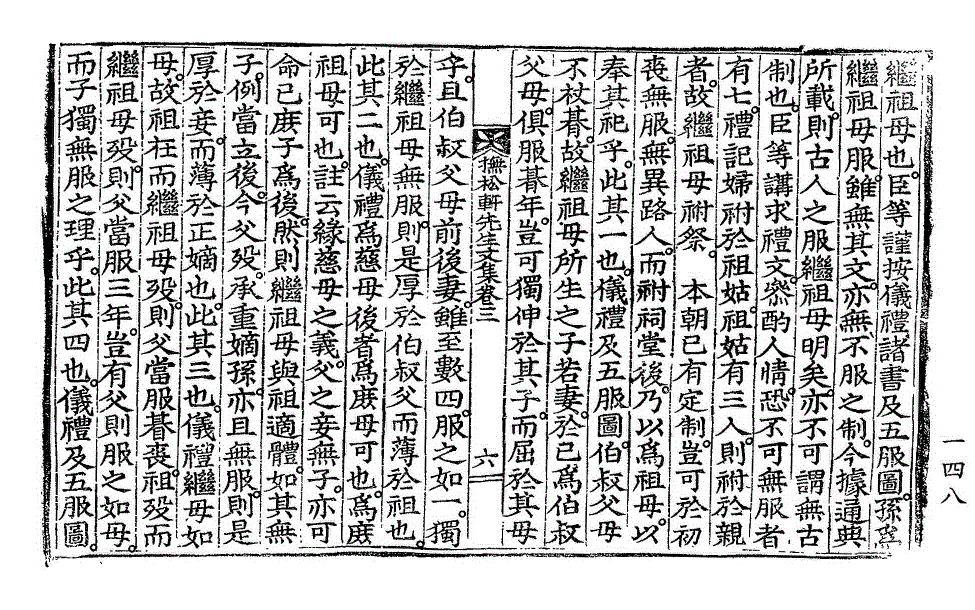 继祖母也。臣等谨按仪礼诸书及五服图。孙为继祖母服。虽无其文。亦无不服之制。今据通典所载。则古人之服继祖母明矣。亦不可谓无古制也。臣等讲求礼文。参酌人情。恐不可无服者有七。礼记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故继祖母祔祭。 本朝已有定制。岂可于初丧无服。无异路人。而祔祠堂后。乃以为祖母。以奉其祀乎。此其一也。仪礼及五服图。伯叔父母不杖期。故继祖母所生之子若妻。于己为伯叔父母。俱服期年。岂可独伸于其子。而屈于其母乎。且伯叔父母前后妻。虽至数四。服之如一。独于继祖母无服。则是厚于伯叔父而薄于祖也。此其二也。仪礼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庶祖母可也。注云缘慈母之义。父之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后。然则继祖母与祖适体。如其无子。例当立后。今父殁。承重嫡孙。亦且无服。则是厚于妾。而薄于正嫡也。此其三也。仪礼继母如母。故祖在而继祖母殁。则父当服期丧。祖殁而继祖母殁。则父当服三年。岂有父则服之如母。而子独无服之理乎。此其四也。仪礼及五服图。
继祖母也。臣等谨按仪礼诸书及五服图。孙为继祖母服。虽无其文。亦无不服之制。今据通典所载。则古人之服继祖母明矣。亦不可谓无古制也。臣等讲求礼文。参酌人情。恐不可无服者有七。礼记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故继祖母祔祭。 本朝已有定制。岂可于初丧无服。无异路人。而祔祠堂后。乃以为祖母。以奉其祀乎。此其一也。仪礼及五服图。伯叔父母不杖期。故继祖母所生之子若妻。于己为伯叔父母。俱服期年。岂可独伸于其子。而屈于其母乎。且伯叔父母前后妻。虽至数四。服之如一。独于继祖母无服。则是厚于伯叔父而薄于祖也。此其二也。仪礼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庶祖母可也。注云缘慈母之义。父之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后。然则继祖母与祖适体。如其无子。例当立后。今父殁。承重嫡孙。亦且无服。则是厚于妾。而薄于正嫡也。此其三也。仪礼继母如母。故祖在而继祖母殁。则父当服期丧。祖殁而继祖母殁。则父当服三年。岂有父则服之如母。而子独无服之理乎。此其四也。仪礼及五服图。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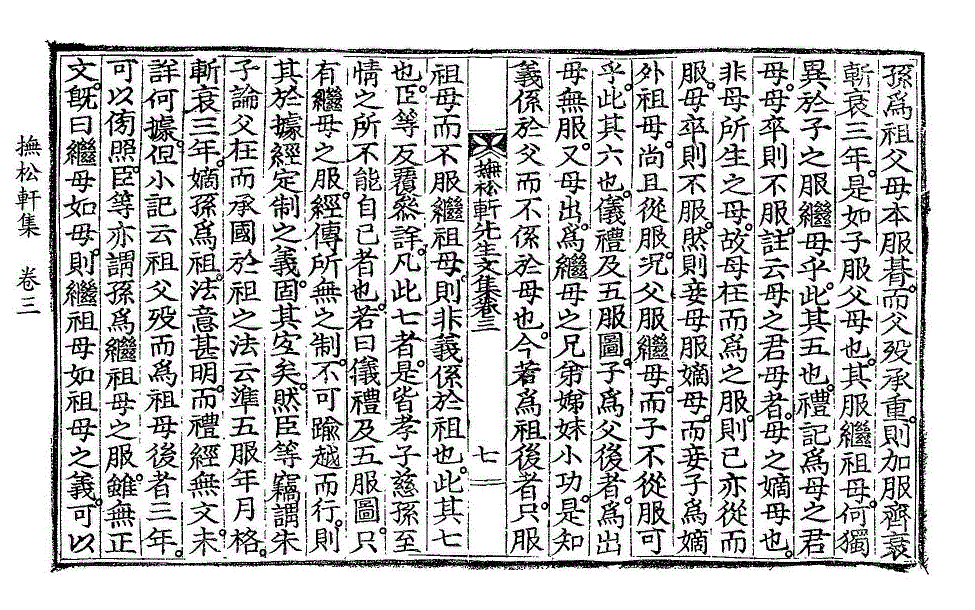 孙为祖父母本服期。而父殁承重。则加服齐衰斩衰三年。是如子服父母也。其服继祖母。何独异于子之服继母乎。此其五也。礼记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注云母之君母者。母之嫡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为之服。则己亦从而服。母卒则不服。然则妾母服嫡母。而妾子为嫡外祖母。尚且从服。况父服继母。而子不从服可乎。此其六也。仪礼及五服图。子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又母出。为继母之兄弟娣妹小功。是知义系于父而不系于母也。今若为祖后者。只服祖母而不服继祖母。则非义系于祖也。此其七也。臣等反覆参详。凡此七者。是皆孝子慈孙至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也。若曰仪礼及五服图。只有继母之服。经传所无之制。不可踰越而行。则其于据经定制之义。固其宜矣。然臣等窃谓朱子论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法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嫡孙为祖。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未详何据。但小记云祖父殁而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傍照。臣等亦谓孙为继祖母之服。虽无正文。既曰继母如母。则继祖母如祖母之义。可以
孙为祖父母本服期。而父殁承重。则加服齐衰斩衰三年。是如子服父母也。其服继祖母。何独异于子之服继母乎。此其五也。礼记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注云母之君母者。母之嫡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为之服。则己亦从而服。母卒则不服。然则妾母服嫡母。而妾子为嫡外祖母。尚且从服。况父服继母。而子不从服可乎。此其六也。仪礼及五服图。子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又母出。为继母之兄弟娣妹小功。是知义系于父而不系于母也。今若为祖后者。只服祖母而不服继祖母。则非义系于祖也。此其七也。臣等反覆参详。凡此七者。是皆孝子慈孙至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也。若曰仪礼及五服图。只有继母之服。经传所无之制。不可踰越而行。则其于据经定制之义。固其宜矣。然臣等窃谓朱子论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法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嫡孙为祖。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未详何据。但小记云祖父殁而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傍照。臣等亦谓孙为继祖母之服。虽无正文。既曰继母如母。则继祖母如祖母之义。可以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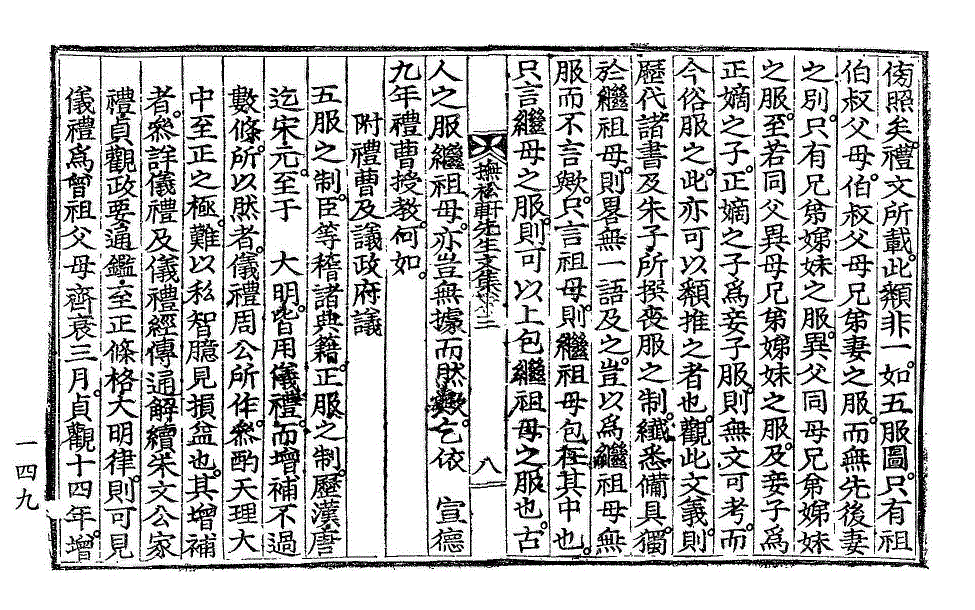 傍照矣。礼文所载。此类非一。如五服图。只有祖伯叔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妻之服。而无先后妻之别。只有兄弟娣妹之服。异父同母兄弟娣妹之服。至若同父异母兄弟娣妹之服。及妾子为正嫡之子。正嫡之子为妾子服。则无文可考。而今俗服之。此亦可以类推之者也。观此文义。则历代诸书及朱子所撰丧服之制。纤悉备具。独于继祖母。则略无一语及之。岂以为继祖母无服而不言欤。只言祖母。则继祖母包在其中也。只言继母之服。则可以上包继祖母之服也。古人之服继祖母。亦岂无据而然欤。乞依 宣德九年礼曹授教。何如。
傍照矣。礼文所载。此类非一。如五服图。只有祖伯叔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妻之服。而无先后妻之别。只有兄弟娣妹之服。异父同母兄弟娣妹之服。至若同父异母兄弟娣妹之服。及妾子为正嫡之子。正嫡之子为妾子服。则无文可考。而今俗服之。此亦可以类推之者也。观此文义。则历代诸书及朱子所撰丧服之制。纤悉备具。独于继祖母。则略无一语及之。岂以为继祖母无服而不言欤。只言祖母。则继祖母包在其中也。只言继母之服。则可以上包继祖母之服也。古人之服继祖母。亦岂无据而然欤。乞依 宣德九年礼曹授教。何如。附礼曹及议政府议
五服之制。臣等稽诸典籍。正服之制。历汉,唐迄宋,元。至于 大明。皆用仪礼。而增补不过数条。所以然者。仪礼周公所作。参酌天理大中至正之极。难以私智臆见损益也。其增补者。参详仪礼及仪礼经传通解续,朱文公家礼,贞观政要,通鉴,至正条格,大明律。则可见仪礼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贞观十四年。增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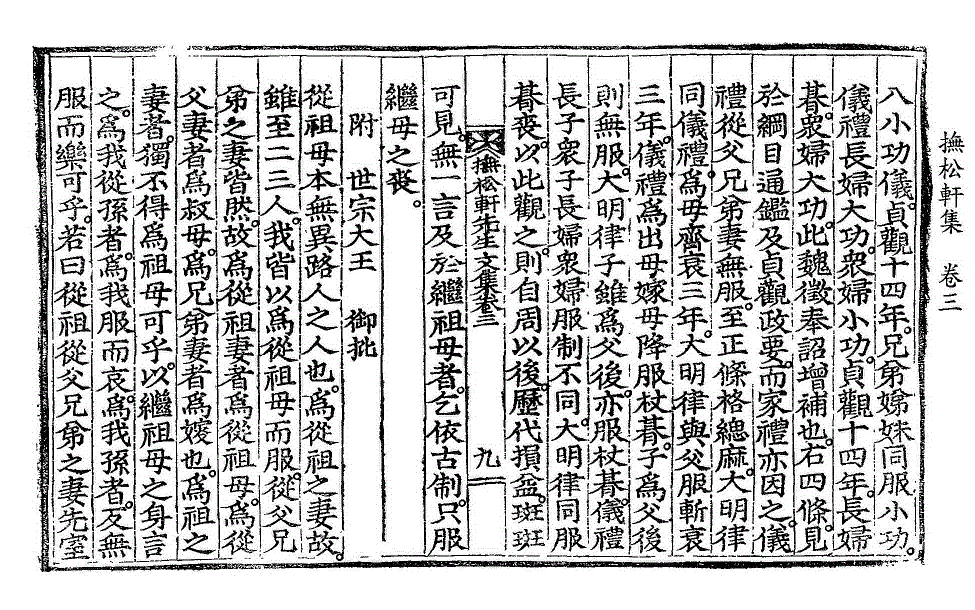 入小功仪。贞观十四年。兄弟娣妹同服小功。仪礼长妇大功。众妇小功。贞观十四年。长妇期。众妇大功。此魏徵奉诏增补也。右四条。见于纲目通鉴及贞观政要。而家礼亦因之。仪礼从父兄弟妻无服。至正条格缌麻。大明律同仪礼。为母齐衰三年。大明律与父服斩衰三年。仪礼为出母,嫁母降服杖期。子为父后则无服。大明律子虽为父后。亦服杖期。仪礼长子众子长妇众妇服制不同。大明律同服期丧。以此观之。则自周以后。历代损益。斑斑可见。无一言及于继祖母者。乞依古制。只服继母之丧。
入小功仪。贞观十四年。兄弟娣妹同服小功。仪礼长妇大功。众妇小功。贞观十四年。长妇期。众妇大功。此魏徵奉诏增补也。右四条。见于纲目通鉴及贞观政要。而家礼亦因之。仪礼从父兄弟妻无服。至正条格缌麻。大明律同仪礼。为母齐衰三年。大明律与父服斩衰三年。仪礼为出母,嫁母降服杖期。子为父后则无服。大明律子虽为父后。亦服杖期。仪礼长子众子长妇众妇服制不同。大明律同服期丧。以此观之。则自周以后。历代损益。斑斑可见。无一言及于继祖母者。乞依古制。只服继母之丧。附 世宗大王 御批
从祖母本无异路人之人也。为从祖之妻故。虽至二三人。我皆以为从祖母而服。从父兄弟之妻皆然。故为从祖妻者为从祖母。为从父妻者为叔母。为兄弟妻者为嫂也。为祖之妻者。独不得为祖母可乎。以继祖母之身言之。为我从孙者。为我服而哀。为我孙者。反无服而乐可乎。若曰从祖从父兄弟之妻先室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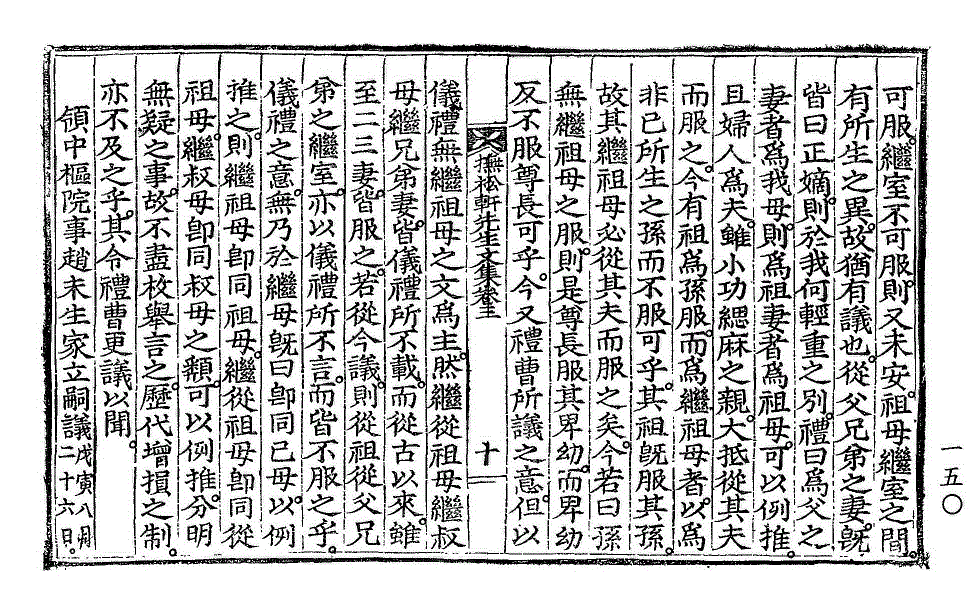 可服。继室不可服。则又未安。祖母继室之间。有所生之异。故犹有议也。从父兄弟之妻。既皆曰正嫡。则于我何轻重之别。礼曰为父之妻者为我母。则为祖妻者为祖母。可以例推。且妇人为夫。虽小功缌麻之亲。大抵从其夫而服之。今有祖为孙服。而为继祖母者。以为非己所生之孙而不服可乎。其祖既服其孙。故其继祖母必从其夫而服之矣。今若曰孙无继祖母之服。则是尊长服其卑幼。而卑幼反不服尊长可乎。今又礼曹所议之意。但以仪礼无继祖母之文为主。然继从祖母继叔母继兄弟妻。皆仪礼所不载。而从古以来。虽至二三妻。皆服之。若从今议。则从祖从父兄弟之继室。亦以仪礼所不言。而皆不服之乎。仪礼之意。无乃于继母既曰即同己母。以例推之。则继祖母即同祖母。继从祖母即同从祖母。继叔母即同叔母之类。可以例推。分明无疑之事。故不尽枚举言之。历代增损之制。亦不及之乎。其令礼曹更议以闻。
可服。继室不可服。则又未安。祖母继室之间。有所生之异。故犹有议也。从父兄弟之妻。既皆曰正嫡。则于我何轻重之别。礼曰为父之妻者为我母。则为祖妻者为祖母。可以例推。且妇人为夫。虽小功缌麻之亲。大抵从其夫而服之。今有祖为孙服。而为继祖母者。以为非己所生之孙而不服可乎。其祖既服其孙。故其继祖母必从其夫而服之矣。今若曰孙无继祖母之服。则是尊长服其卑幼。而卑幼反不服尊长可乎。今又礼曹所议之意。但以仪礼无继祖母之文为主。然继从祖母继叔母继兄弟妻。皆仪礼所不载。而从古以来。虽至二三妻。皆服之。若从今议。则从祖从父兄弟之继室。亦以仪礼所不言。而皆不服之乎。仪礼之意。无乃于继母既曰即同己母。以例推之。则继祖母即同祖母。继从祖母即同从祖母。继叔母即同叔母之类。可以例推。分明无疑之事。故不尽枚举言之。历代增损之制。亦不及之乎。其令礼曹更议以闻。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1H 页
 领中枢院事赵末生家立嗣议(戊寅八月二十六日。与礼曹兼判书右赞成黄守身,判书李承孙联名。○按先生之久已在外。而与于是议。岂以曾有礼议 除拜之故也欤。)
领中枢院事赵末生家立嗣议(戊寅八月二十六日。与礼曹兼判书右赞成黄守身,判书李承孙联名。○按先生之久已在外。而与于是议。岂以曾有礼议 除拜之故也欤。)卒领中枢院事赵末生舍其嫡孙渶。以第三子瑾奉祀。 上命议政府礼曹议之。
谨稽续礼典家庙祭礼条云礼无次子立庙之文。若长子长孙孱劣。肩居人家。虽有宗人相助。终不得立祠堂者。许令长子立之。其长子长孙。今虽单弱无依。终可立祠堂者。次子依元礼不能立庙者例。择净室一间。以奉神主。待长子长孙立祠堂。奉还神主。自馀长子长孙虽废疾者。苟有宅舍。皆立祠堂。至祭时。令次子代行。如文公家礼。祭初就位参神。休于他所。祭终复位辞神。此乃稽古酌今。合于人情天理。其法至为严密。然则长子孙虽有废疾。不得以他子立祠。昭然可知。虽曰长孙渶不堪主祀。然不令次子瓒主祀而与之。第三子瑾情涉私爱。非至公之意明矣。况钟爱于季。人之常情。今托称从权。擅改国家令典与万世宗子之法。轻扰天伦。则后世为人父者。奉祀家舍田民。欲传钟爱之子主祀。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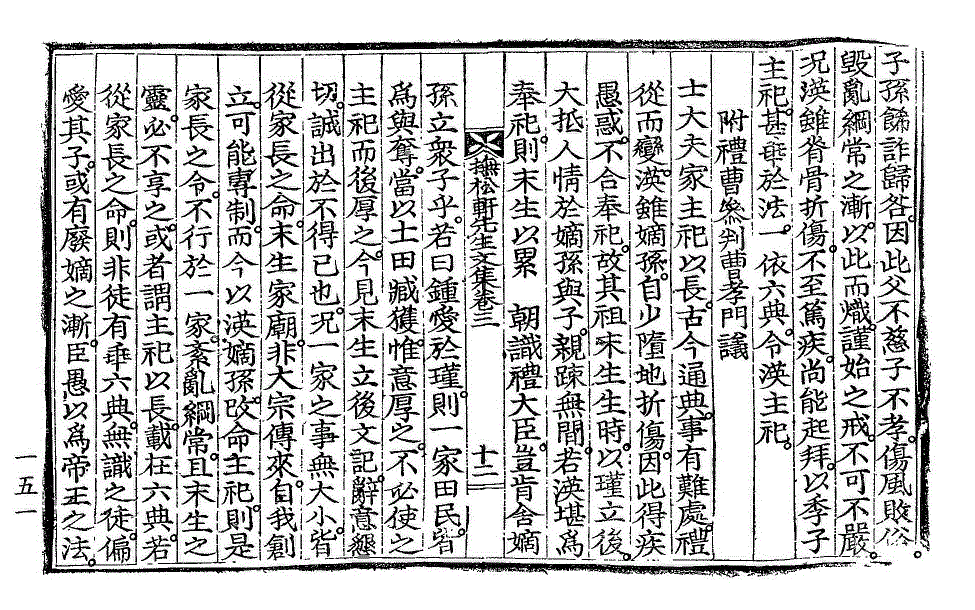 子孙饰诈归咎。因此父不慈子不孝。伤风败俗。毁乱纲常之渐。以此而炽。谨始之戒。不可不严。况渶虽脊骨折伤。不至笃疾。尚能起拜。以季子主祀。甚乖于法。一依六典。令渶主祀。
子孙饰诈归咎。因此父不慈子不孝。伤风败俗。毁乱纲常之渐。以此而炽。谨始之戒。不可不严。况渶虽脊骨折伤。不至笃疾。尚能起拜。以季子主祀。甚乖于法。一依六典。令渶主祀。附礼曹参判曹孝门议
士大夫家主祀以长。古今通典。事有难处。礼从而变。渶虽嫡孙。自少堕地折伤。因此得疾愚惑。不合奉祀。故其祖末生生时。以瑾立后。大抵人情于嫡孙与子。亲疏无间。若渶堪为奉祀。则末生以累 朝识礼大臣。岂肯舍嫡孙立众子乎。若曰钟爱于瑾。则一家田民。皆为与夺。当以土田臧获。惟意厚之。不必使之主祀而后厚之。今见末生立后文记。辞意恳切。诚出于不得已也。况一家之事无大小。皆从家长之命。末生家庙。非大宗传来。自我创立。可能专制。而今以渶嫡孙。改命主祀。则是家长之令。不行于一家。紊乱纲常。且末生之灵。必不享之。或者谓主祀以长。载在六典。若从家长之命。则非徒有乖六典。无识之徒。偏爱其子。或有废嫡之渐。臣愚以为帝王之法。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2H 页
 权经并用。若拘六典之法。而废祖父之命。则悖逆之徒。恃法自恣。非细故也。且古今天下。不慈之父无闻。而不孝子孙常多。长子若孙。非有大故。则虽甚无道。不至废弃。以此观之。祖父废嫡之萌。子孙悖逆之渐。轻重有异。帝王维持世道。不过扶植纲常。请末生主祀。依其情愿。令瑾主祀。
权经并用。若拘六典之法。而废祖父之命。则悖逆之徒。恃法自恣。非细故也。且古今天下。不慈之父无闻。而不孝子孙常多。长子若孙。非有大故。则虽甚无道。不至废弃。以此观之。祖父废嫡之萌。子孙悖逆之渐。轻重有异。帝王维持世道。不过扶植纲常。请末生主祀。依其情愿。令瑾主祀。附右议政姜孟卿及右参赞成奉祖等议。
奉祀以长。实古今之常经。而择人以后。亦一时之权宜也。经权虽异。而其要则在乎当理而已矣。若长子孙废疾愚惑而不堪奉祀。则谓之以长。而付后事于无用之人乎。此不得不用其权也。假使末生身为嫡长。奉祖祢祠堂。而为祖祢择人。亦不可谓之擅改。况末生身为始祖。而其主祀者。非祖祢之嫡长者乎。且先儒曰。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乎。且曰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末生平生观嫡孙渶有疾。于亡妻神主傍题。俾书三子瑾之名。手草改后之文。则非末生之乱命明矣。今渶虽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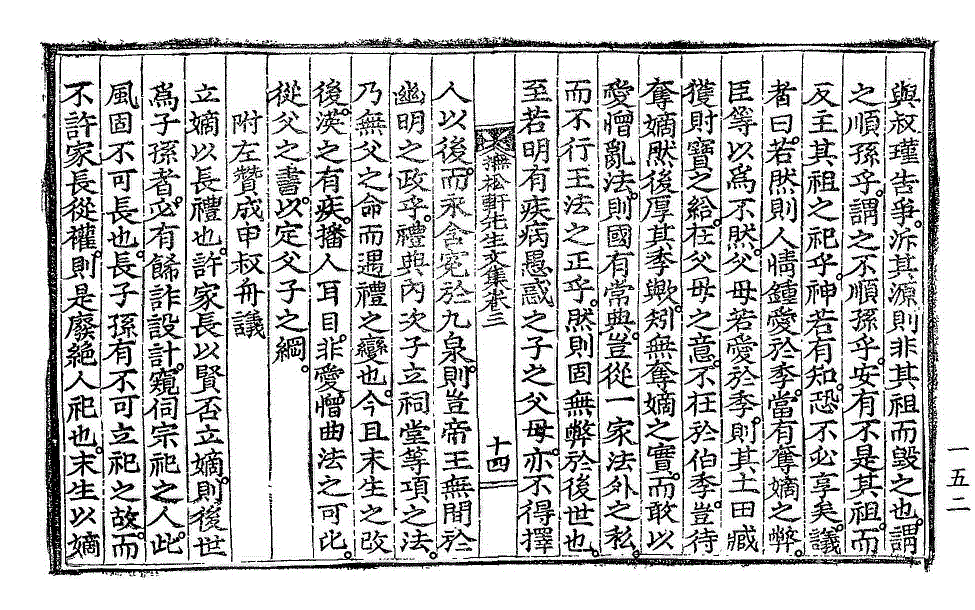 与叔瑾告争。溯其源则非其祖而毁之也。谓之顺孙乎。谓之不顺孙乎。安有不是其祖。而反主其祖之祀乎。神若有知。恐不必享矣。议者曰。若然则人情钟爱于季。当有夺嫡之弊。臣等以为不然。父母若爱于季。则其土田臧获财宝之给。在父母之意。不在于伯季。岂待夺嫡然后厚其季欤。矧无夺嫡之实。而敢以爱憎乱法。则国有常典。岂从一家法外之私。而不行王法之正乎。然则固无弊于后世也。至若明有疾病愚惑之子之父母。亦不得择人以后。而永含冤于九泉。则岂帝王无间于幽明之政乎。礼典内次子立祠堂等项之法。乃无父之命而遇礼之变也。今且末生之改后。渶之有疾。播人耳目。非爱憎曲法之可比。从父之书。以定父子之纲。
与叔瑾告争。溯其源则非其祖而毁之也。谓之顺孙乎。谓之不顺孙乎。安有不是其祖。而反主其祖之祀乎。神若有知。恐不必享矣。议者曰。若然则人情钟爱于季。当有夺嫡之弊。臣等以为不然。父母若爱于季。则其土田臧获财宝之给。在父母之意。不在于伯季。岂待夺嫡然后厚其季欤。矧无夺嫡之实。而敢以爱憎乱法。则国有常典。岂从一家法外之私。而不行王法之正乎。然则固无弊于后世也。至若明有疾病愚惑之子之父母。亦不得择人以后。而永含冤于九泉。则岂帝王无间于幽明之政乎。礼典内次子立祠堂等项之法。乃无父之命而遇礼之变也。今且末生之改后。渶之有疾。播人耳目。非爱憎曲法之可比。从父之书。以定父子之纲。附左赞成申叔舟议
立嫡以长礼也。许家长以贤否立嫡。则后世为子孙者。必有饰诈设计。窥伺宗祀之人。此风固不可长也。长子孙有不可立祀之故。而不许家长从权。则是废绝人祀也。末生以嫡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3H 页
 孙渶有疾。择于子而立瑾。末生既死。渶争嫡。于理不顺。六典立祠堂之法。非为有家长之命者。今不可必令死父之命。复嫡其孙也。宜从末生之遗命。但窥伺夺宗之风。不可不为之防。自今长子孙有不得主祀之故。令家长告于官。明其实。然后许令次子孙主祀。永以为法。
孙渶有疾。择于子而立瑾。末生既死。渶争嫡。于理不顺。六典立祠堂之法。非为有家长之命者。今不可必令死父之命。复嫡其孙也。宜从末生之遗命。但窥伺夺宗之风。不可不为之防。自今长子孙有不得主祀之故。令家长告于官。明其实。然后许令次子孙主祀。永以为法。附左参赞朴仲孙议
士大夫一家之政。容或有以私废公者。 国家不知则已。今已告争。当以经常之典处之。渶不至笃疾。可能主祀。依六典。以严宗子之法。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对策
重试对策(丁卯八月)
[法立弊生]
王若曰。法立弊生。古今之通患也。东汉因都试起兵之弊。省郡国都尉。罢车骑材官。宋太祖睹汉唐藩镇之强。至一兵一财。皆朝廷自制之。然东汉有内重外轻之失。宋有武略不竞之患。汉文纳贾谊之言。礼貌大臣。不使施刑。其流之弊。大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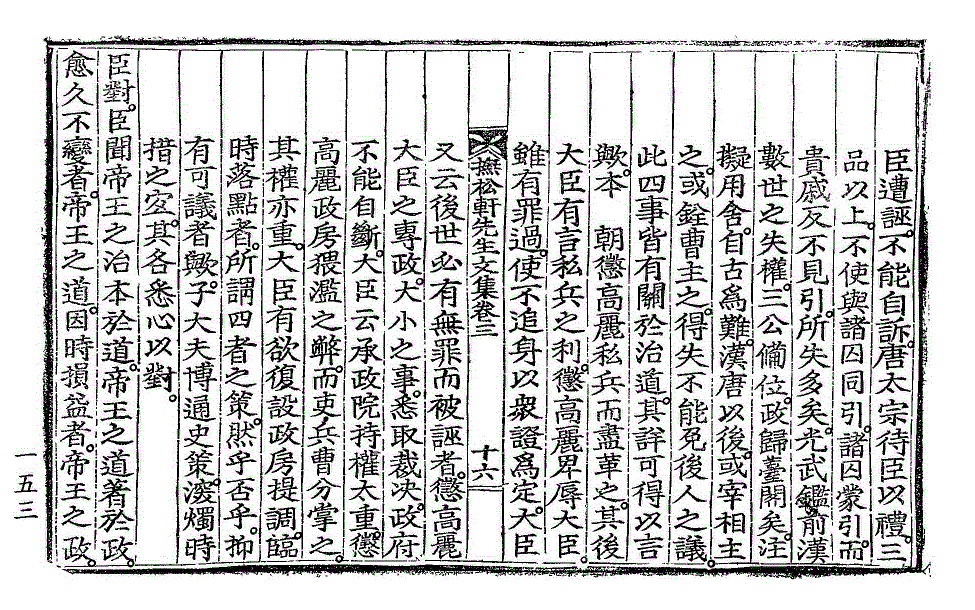 臣遭诬。不能自诉。唐太宗待臣以礼。三品以上。不使与诸囚同引。诸囚蒙引。而贵戚反不见引。所失多矣。光武鉴前汉数世之失权。三公备位。政归薹阁矣。注拟用舍。自古为难。汉唐以后。或宰相主之。或铨曹主之。得失不能免后人之议。此四事皆有关于治道。其详可得以言欤。本 朝惩高丽私兵而尽革之。其后大臣有言私兵之利。惩高丽卑辱大臣。虽有罪过。使不追身以众證为定。大臣又云后世必有无罪而被诬者。惩高丽大臣之专政。大小之事。悉取裁决。政府不能自断。大臣云承政院持权太重。惩高丽政房猥滥之弊。而吏,兵曹分掌之。其权亦重。大臣有欲复设政房提调。临时落点者。所谓四者之策。然乎否乎。抑有可议者欤。子大夫博通史策。深烛时措之宜。其各悉心以对。
臣遭诬。不能自诉。唐太宗待臣以礼。三品以上。不使与诸囚同引。诸囚蒙引。而贵戚反不见引。所失多矣。光武鉴前汉数世之失权。三公备位。政归薹阁矣。注拟用舍。自古为难。汉唐以后。或宰相主之。或铨曹主之。得失不能免后人之议。此四事皆有关于治道。其详可得以言欤。本 朝惩高丽私兵而尽革之。其后大臣有言私兵之利。惩高丽卑辱大臣。虽有罪过。使不追身以众證为定。大臣又云后世必有无罪而被诬者。惩高丽大臣之专政。大小之事。悉取裁决。政府不能自断。大臣云承政院持权太重。惩高丽政房猥滥之弊。而吏,兵曹分掌之。其权亦重。大臣有欲复设政房提调。临时落点者。所谓四者之策。然乎否乎。抑有可议者欤。子大夫博通史策。深烛时措之宜。其各悉心以对。臣对。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著于政。愈久不变者。帝王之道。因时损益者。帝王之政。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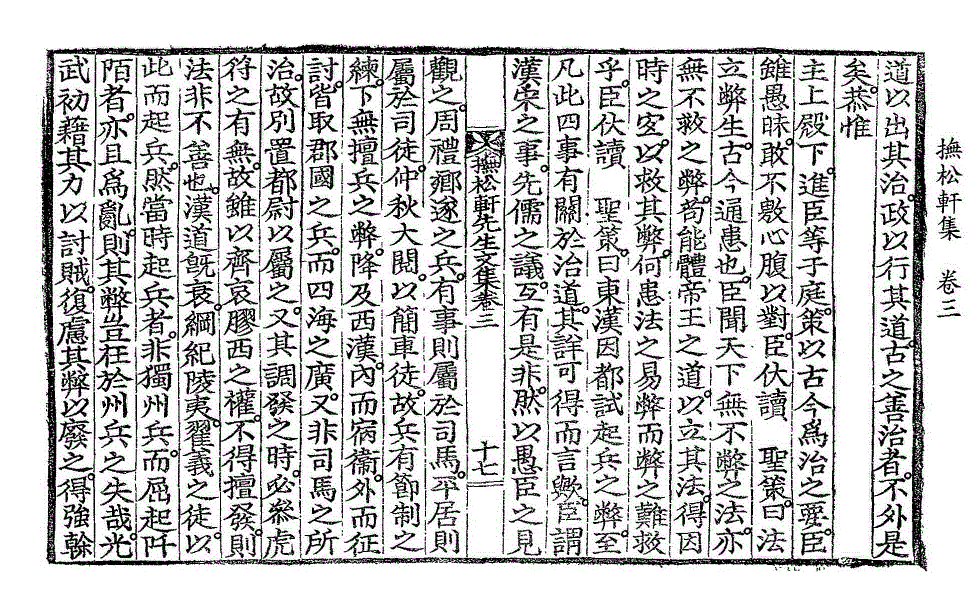 道以出其治。政以行其道。古之善治者。不外是矣。恭惟 主上殿下。进臣等于庭。策以古今为治之要。臣虽愚昧。敢不敷心腹以对。臣伏读 圣策。曰法立弊生。古今通患也。臣闻天下无不弊之法。亦无不救之弊。苟能体帝王之道。以立其法。得因时之宜。以救其弊。何患法之易弊而弊之难救乎。臣伏读 圣策。曰东汉因都试起兵之弊。至凡此四事有关于治道。其详可得而言欤。臣谓汉,宋之事。先儒之议。互有是非。然以愚臣之见观之。周礼乡遂之兵。有事则属于司马。平居则属于司徒。仲秋大阅。以简车徒。故兵有节制之练。下无擅兵之弊。降及西汉。内而宿卫。外而征讨。皆取郡国之兵。而四海之广。又非司马之所治。故别置都尉以属之。又其调发之时。必参虎符之有无。故虽以齐哀胶西之权。不得擅发。则法非不善也。汉道既衰。纲纪陵夷。翟义之徒。以此而起兵。然当时起兵者。非独州兵。而屈起阡陌者。亦且为乱。则其弊岂在于州兵之失哉。光武初藉其力以讨贼。复虑其弊以废之。得强干
道以出其治。政以行其道。古之善治者。不外是矣。恭惟 主上殿下。进臣等于庭。策以古今为治之要。臣虽愚昧。敢不敷心腹以对。臣伏读 圣策。曰法立弊生。古今通患也。臣闻天下无不弊之法。亦无不救之弊。苟能体帝王之道。以立其法。得因时之宜。以救其弊。何患法之易弊而弊之难救乎。臣伏读 圣策。曰东汉因都试起兵之弊。至凡此四事有关于治道。其详可得而言欤。臣谓汉,宋之事。先儒之议。互有是非。然以愚臣之见观之。周礼乡遂之兵。有事则属于司马。平居则属于司徒。仲秋大阅。以简车徒。故兵有节制之练。下无擅兵之弊。降及西汉。内而宿卫。外而征讨。皆取郡国之兵。而四海之广。又非司马之所治。故别置都尉以属之。又其调发之时。必参虎符之有无。故虽以齐哀胶西之权。不得擅发。则法非不善也。汉道既衰。纲纪陵夷。翟义之徒。以此而起兵。然当时起兵者。非独州兵。而屈起阡陌者。亦且为乱。则其弊岂在于州兵之失哉。光武初藉其力以讨贼。复虑其弊以废之。得强干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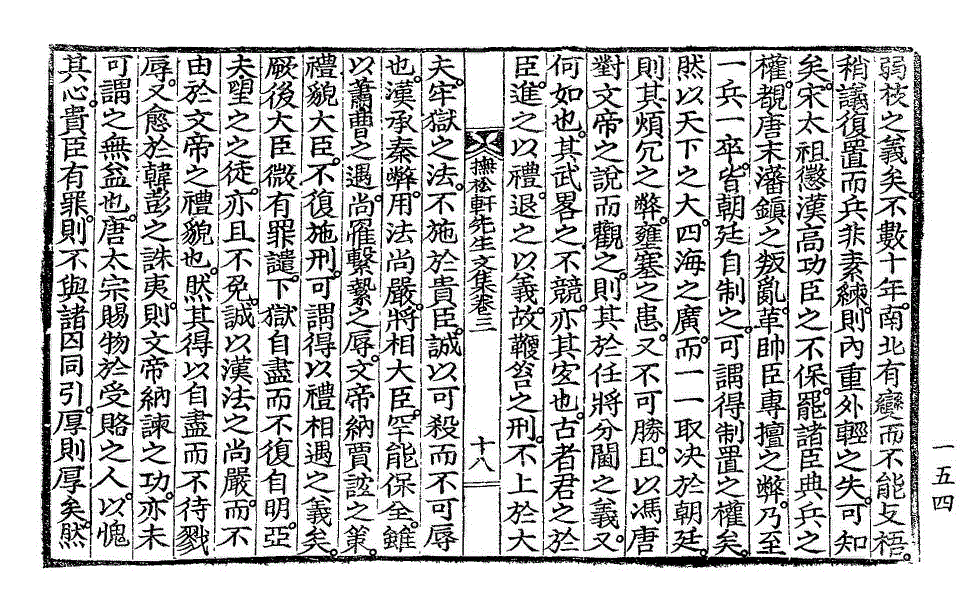 弱枝之义矣。不数十年。南北有变而不能支梧。稍议复置而兵非素练。则内重外轻之失。可知矣。宋太祖惩汉高功臣之不保。罢诸臣典兵之权。睹唐末藩镇之叛乱。革帅臣专擅之弊。乃至一兵一卒。皆朝廷自制之。可谓得制置之权矣。然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而一一取决于朝廷。则其烦冗之弊。壅塞之患。又不可胜。且以冯唐对文帝之说而观之。则其于任将分阃之义。又何如也。其武略之不竞。亦其宜也。古者君之于臣。进之以礼。退之以义。故鞭笞之刑。不上于大夫。牢狱之法。不施于贵臣。诚以可杀而不可辱也。汉承秦弊。用法尚严。将相大臣。罕能保全。虽以萧,曹之遇。尚罹系絷之辱。文帝纳贾谊之策。礼貌大臣。不复施刑。可谓得以礼相遇之义矣。厥后大臣微有罪谴。下狱自尽而不复自明。亚夫,望之之徒亦且不免。诚以汉法之尚严。而不由于文帝之礼貌也。然其得以自尽而不待戮辱。又愈于韩,彭之诛夷。则文帝纳谏之功。亦未可谓之无益也。唐太宗赐物于受赂之人。以愧其心。贵臣有罪。则不与诸囚同引。厚则厚矣。然
弱枝之义矣。不数十年。南北有变而不能支梧。稍议复置而兵非素练。则内重外轻之失。可知矣。宋太祖惩汉高功臣之不保。罢诸臣典兵之权。睹唐末藩镇之叛乱。革帅臣专擅之弊。乃至一兵一卒。皆朝廷自制之。可谓得制置之权矣。然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而一一取决于朝廷。则其烦冗之弊。壅塞之患。又不可胜。且以冯唐对文帝之说而观之。则其于任将分阃之义。又何如也。其武略之不竞。亦其宜也。古者君之于臣。进之以礼。退之以义。故鞭笞之刑。不上于大夫。牢狱之法。不施于贵臣。诚以可杀而不可辱也。汉承秦弊。用法尚严。将相大臣。罕能保全。虽以萧,曹之遇。尚罹系絷之辱。文帝纳贾谊之策。礼貌大臣。不复施刑。可谓得以礼相遇之义矣。厥后大臣微有罪谴。下狱自尽而不复自明。亚夫,望之之徒亦且不免。诚以汉法之尚严。而不由于文帝之礼貌也。然其得以自尽而不待戮辱。又愈于韩,彭之诛夷。则文帝纳谏之功。亦未可谓之无益也。唐太宗赐物于受赂之人。以愧其心。贵臣有罪。则不与诸囚同引。厚则厚矣。然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5H 页
 其不能见引而取辨于疑似之间。定罪于他人之口。虽以刘洎之无罪而死。不能明。用法之弊。或至于此。然事非当代。未暇详也。当于当今之事论之乎。古者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而庶务张矣。夫以三公而不亲细事。况天子乎。光武惩西汉大臣之专权。亲决庶务。遂至三公备位。而权归近臣。明帝继体。好察庶事。故吏事之讥。撞郎之诮。载于史传。奚足贵乎。铨选重任也。人材之进退。治道之隆替系焉。汉唐以后。职无定官。或委宰相。或委铨曹。各得一时之权宜。以成一代之治道。主之者得其人则其职举。主之者失其人则其职废。在人而不在于官。亦非当代之事。未暇详也。臣伏读 圣策。曰。 本朝惩高丽私兵之弊。至所谓四者之策。然乎否乎。抑有可议者欤。臣闻国之有兵。所以备宿卫御㬥乱也。古者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晋之六卿。鲁之三家。俱为覆辙。前朝之季。巨家大族。专擅兵权。各立私兵。尾大难掉。迤至国初。尚有其袭。 圣朝奋兴。一革其弊归之军府。此乃万世之大法也。其言私兵之利者。乃踵覆辙之轨者也。夫以 圣
其不能见引而取辨于疑似之间。定罪于他人之口。虽以刘洎之无罪而死。不能明。用法之弊。或至于此。然事非当代。未暇详也。当于当今之事论之乎。古者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而庶务张矣。夫以三公而不亲细事。况天子乎。光武惩西汉大臣之专权。亲决庶务。遂至三公备位。而权归近臣。明帝继体。好察庶事。故吏事之讥。撞郎之诮。载于史传。奚足贵乎。铨选重任也。人材之进退。治道之隆替系焉。汉唐以后。职无定官。或委宰相。或委铨曹。各得一时之权宜。以成一代之治道。主之者得其人则其职举。主之者失其人则其职废。在人而不在于官。亦非当代之事。未暇详也。臣伏读 圣策。曰。 本朝惩高丽私兵之弊。至所谓四者之策。然乎否乎。抑有可议者欤。臣闻国之有兵。所以备宿卫御㬥乱也。古者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晋之六卿。鲁之三家。俱为覆辙。前朝之季。巨家大族。专擅兵权。各立私兵。尾大难掉。迤至国初。尚有其袭。 圣朝奋兴。一革其弊归之军府。此乃万世之大法也。其言私兵之利者。乃踵覆辙之轨者也。夫以 圣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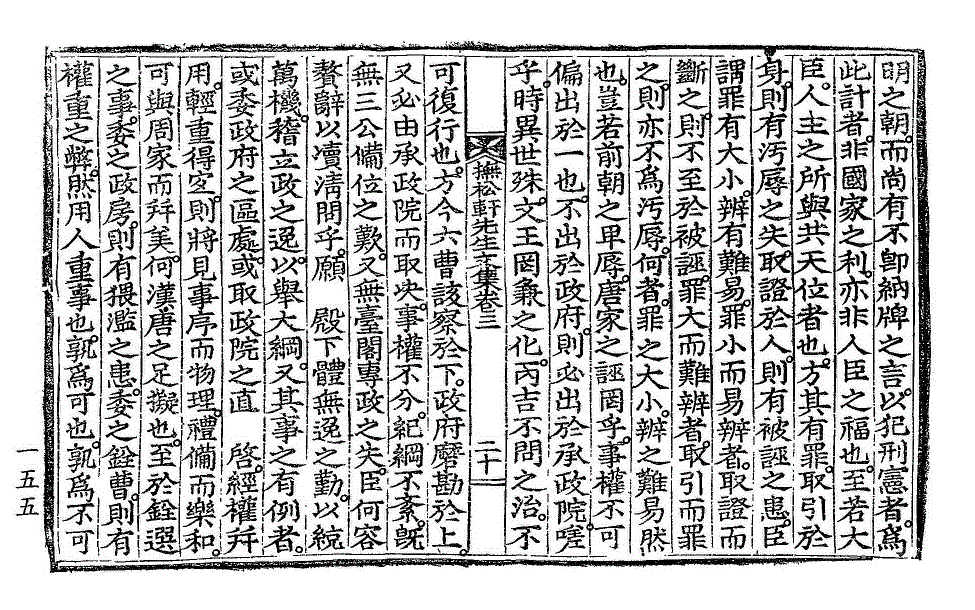 明之朝。而尚有不即纳牌之言。以犯刑宪者。为此计者。非国家之利。亦非人臣之福也。至若大臣。人主之所与共天位者也。方其有罪。取引于身。则有污辱之失。取證于人。则有被诬之患。臣谓罪有大小。辨有难易。罪小而易辨者。取證而断之。则不至于被诬。罪大而难辨者。取引而罪之。则亦不为污辱。何者。罪之大小。辨之难易然也。岂若前朝之卑辱。唐家之诬罔乎。事权不可偏出于一也。不出于政府。则必出于承政院。嗟乎。时异世殊。文王罔兼之化。丙吉不问之治。不可复行也。方今六曹该察于下。政府磨勘于上。又必由承政院而取决。事权不分。纪纲不紊。既无三公备位之叹。又无台阁专政之失。臣何容赘辞以渎清问乎。愿 殿下体无逸之勤。以统万机。稽立政之逸。以举大纲。又其事之有例者。或委政府之区处。或取政院之直 启。经权并用。轻重得宜。则将见事序而物理。礼备而乐和。可与周家而并美。何汉,唐之足拟也。至于铨选之事。委之政房。则有猥滥之患。委之铨曹。则有权重之弊。然用人重事也。孰为可也。孰为不可
明之朝。而尚有不即纳牌之言。以犯刑宪者。为此计者。非国家之利。亦非人臣之福也。至若大臣。人主之所与共天位者也。方其有罪。取引于身。则有污辱之失。取證于人。则有被诬之患。臣谓罪有大小。辨有难易。罪小而易辨者。取證而断之。则不至于被诬。罪大而难辨者。取引而罪之。则亦不为污辱。何者。罪之大小。辨之难易然也。岂若前朝之卑辱。唐家之诬罔乎。事权不可偏出于一也。不出于政府。则必出于承政院。嗟乎。时异世殊。文王罔兼之化。丙吉不问之治。不可复行也。方今六曹该察于下。政府磨勘于上。又必由承政院而取决。事权不分。纪纲不紊。既无三公备位之叹。又无台阁专政之失。臣何容赘辞以渎清问乎。愿 殿下体无逸之勤。以统万机。稽立政之逸。以举大纲。又其事之有例者。或委政府之区处。或取政院之直 启。经权并用。轻重得宜。则将见事序而物理。礼备而乐和。可与周家而并美。何汉,唐之足拟也。至于铨选之事。委之政房。则有猥滥之患。委之铨曹。则有权重之弊。然用人重事也。孰为可也。孰为不可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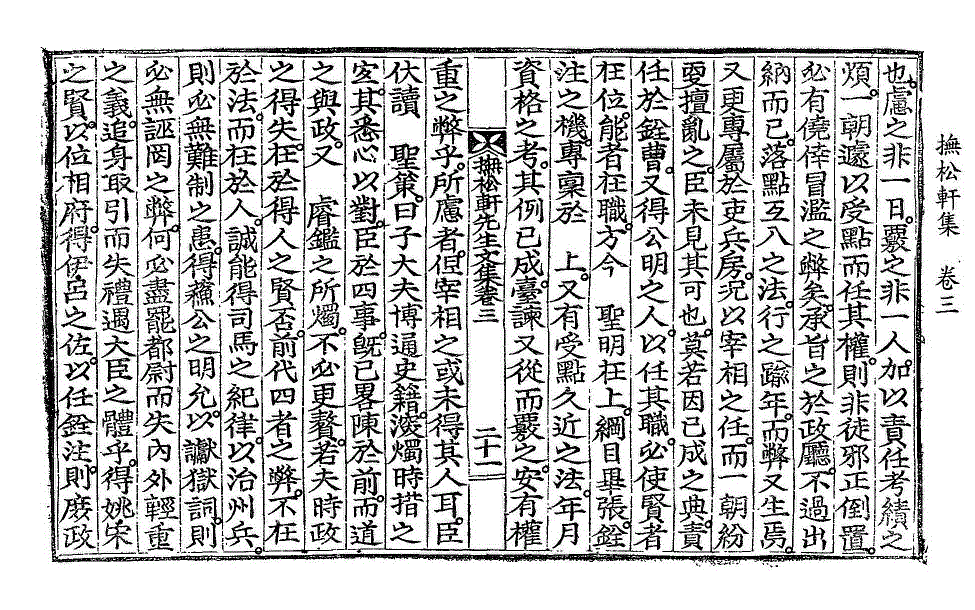 也。虑之非一日。覈之非一人。加以责任考绩之烦。一朝遽以受点而任其权。则非徒邪正倒置。必有侥倖冒滥之弊矣。承旨之于政厅。不过出纳而已。落点互入之法。行之踰年。而弊又生焉。又更专属于吏兵房。况以宰相之任。而一朝纷更擅乱之。臣未见其可也。莫若因已成之典。责任于铨曹。又得公明之人。以任其职。必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方今 圣明在上。纲目毕张。铨注之机。专禀于 上。又有受点久近之法。年月资格之考。其例已成。台谏又从而覈之。安有权重之弊乎。所虑者。但宰相之或未得其人耳。臣伏读 圣策。曰子大夫博通史籍。深烛时措之宜。其悉心以对。臣于四事。既已略陈于前。而道之与政。又 睿鉴之所烛。不必更赘。若夫时政之得失。在于得人之贤否。前代四者之弊。不在于法。而在于人。诚能得司马之纪律。以治州兵。则必无难制之患。得苏公之明允。以谳狱词。则必无诬罔之弊。何必尽罢都尉而失内外轻重之义。追身取引而失礼遇大臣之体乎。得姚,宋之贤。以位相府。得伊,吕之佐。以任铨注。则庶政
也。虑之非一日。覈之非一人。加以责任考绩之烦。一朝遽以受点而任其权。则非徒邪正倒置。必有侥倖冒滥之弊矣。承旨之于政厅。不过出纳而已。落点互入之法。行之踰年。而弊又生焉。又更专属于吏兵房。况以宰相之任。而一朝纷更擅乱之。臣未见其可也。莫若因已成之典。责任于铨曹。又得公明之人。以任其职。必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方今 圣明在上。纲目毕张。铨注之机。专禀于 上。又有受点久近之法。年月资格之考。其例已成。台谏又从而覈之。安有权重之弊乎。所虑者。但宰相之或未得其人耳。臣伏读 圣策。曰子大夫博通史籍。深烛时措之宜。其悉心以对。臣于四事。既已略陈于前。而道之与政。又 睿鉴之所烛。不必更赘。若夫时政之得失。在于得人之贤否。前代四者之弊。不在于法。而在于人。诚能得司马之纪律。以治州兵。则必无难制之患。得苏公之明允。以谳狱词。则必无诬罔之弊。何必尽罢都尉而失内外轻重之义。追身取引而失礼遇大臣之体乎。得姚,宋之贤。以位相府。得伊,吕之佐。以任铨注。则庶政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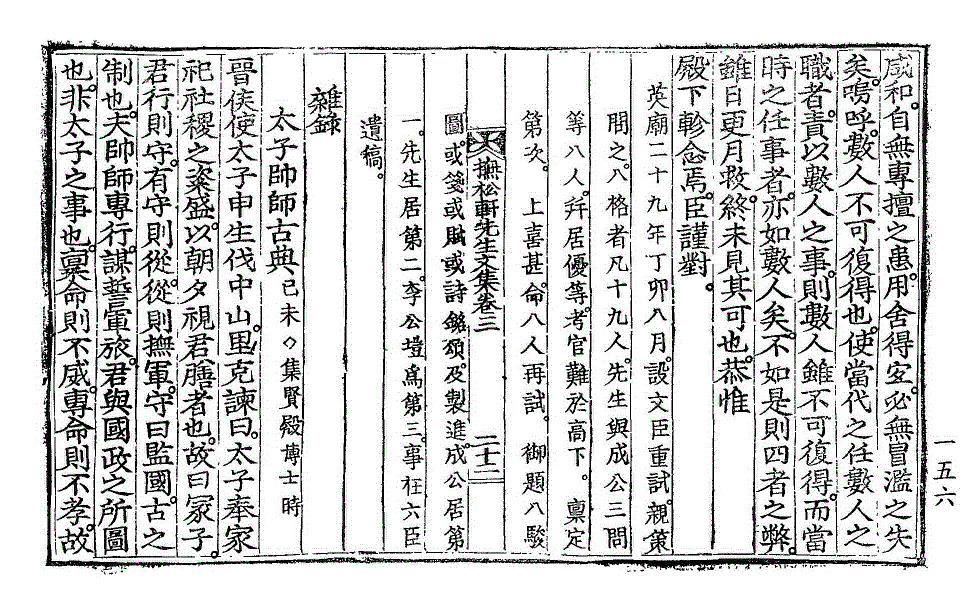 咸和。自无专擅之患。用舍得宜。必无冒滥之失矣。呜呼。数人不可复得也。使当代之任数人之职者。责以数人之事。则数人虽不可复得。而当时之任事者。亦如数人矣。不如是则四者之弊。虽日更月救。终未见其可也。恭惟 殿下轸念焉。臣谨对。
咸和。自无专擅之患。用舍得宜。必无冒滥之失矣。呜呼。数人不可复得也。使当代之任数人之职者。责以数人之事。则数人虽不可复得。而当时之任事者。亦如数人矣。不如是则四者之弊。虽日更月救。终未见其可也。恭惟 殿下轸念焉。臣谨对。( 英庙二十九年丁卯八月。设文臣重试。亲策问之。入格者凡十九人。先生与成公三问等八人。并居优等。考官难于高下。 禀定第次。 上喜甚。命八人再试。 御题八骏图。或笺或赋或诗铭颂。及制进。成公居第一。先生居第二。李公垲为第三。事在六臣遗稿。)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杂录
太子帅师古典(己未○集贤殿博士时)
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中山。里克谏曰。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则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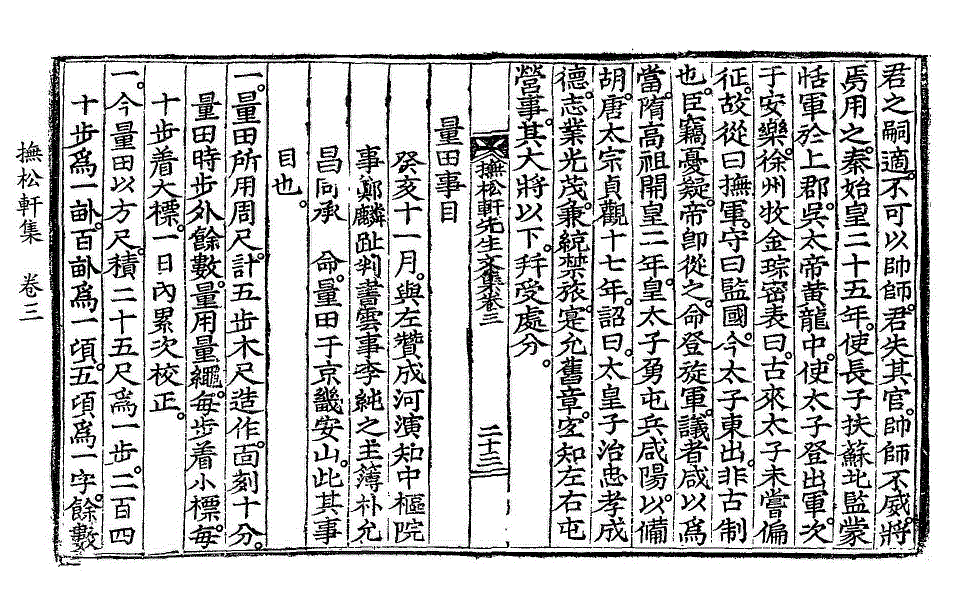 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秦始皇二十五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吴太帝黄龙中。使太子登出军。次于安乐。徐州牧金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臣窃忧疑。帝即从之。命登旋军。议者咸以为当。隋高祖开皇二年。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唐太宗贞观十七年。诏曰。太皇子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兼统禁旅。寔允旧章。宜知左右屯营事。其大将以下。并受处分。
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秦始皇二十五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吴太帝黄龙中。使太子登出军。次于安乐。徐州牧金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臣窃忧疑。帝即从之。命登旋军。议者咸以为当。隋高祖开皇二年。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唐太宗贞观十七年。诏曰。太皇子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兼统禁旅。寔允旧章。宜知左右屯营事。其大将以下。并受处分。量田事目
癸亥十一月。与左赞成河演,知中枢院事郑麟趾,判书云事李纯之,主簿朴允昌同承 命。量田于京畿安山。此其事目也。
一。量田所用周尺。计五步木尺造作。面刻十分。量田时步外馀数。量用量绳。每步着小标。每十步着大标。一日内累次校正。
一。今量田以方尺。积二十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五顷为一字。馀数
抚松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57L 页
 不用。
不用。一。山谷及陵坂倾侧。水田则塍最多者。实积减二十分之一。次多者减三十分之一。又次者减四十分之一。平地不在此限。
一。私处家舍基地及苧楮莞田果园,㯃林,竹林等。凡有利益处。以他田之例量之。若公处寺院基地。毋令并量。
一。一人所耕连伏者。虽曾歧而分之。听其自愿。都量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