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x 页
枫皋集卷之十六
杂著
杂著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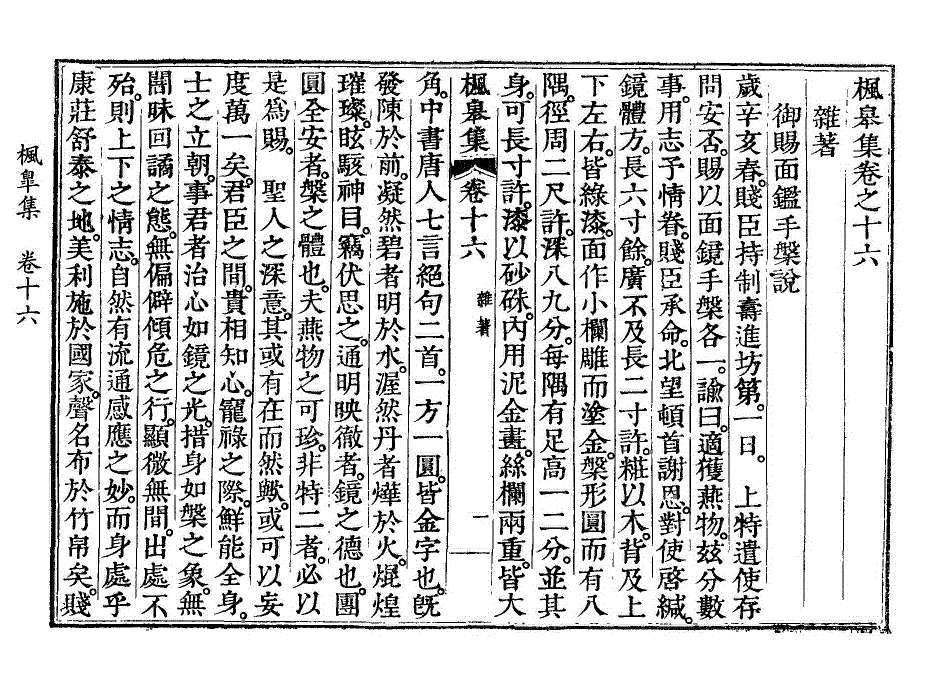 御赐面鉴手槃说
御赐面鉴手槃说岁辛亥春。贱臣持制寿进坊第。一日。 上特遣使存问安否。赐以面镜手槃各一。谕曰。适获燕物。玆分数事。用志予情眷。贱臣承命。北望顿首谢恩。对使启缄。镜体方。长六寸馀。广不及长二寸许。妆以木。背及上下左右。皆绿漆。面作小栏雕而涂金。槃形圆而有八隅。径周二尺许。深八九分。每隅有足高一二分。并其身。可长寸许。漆以砂朱。内用泥金画。丝栏两重。皆大角。中书唐人七言绝句二首。一方一圆。皆金字也。既发陈于前。凝然碧者明于水。渥然丹者烨于火。焜煌璀璨。眩骇神目。窃伏思之。通明映彻者。镜之德也。团圆全安者。槃之体也。夫燕物之可珍。非特二者。必以是为赐。 圣人之深意。其或有在而然欤。或可以妄度万一矣。君臣之间。贵相知心。宠禄之际。鲜能全身。士之立朝。事君者治心如镜之光。措身如槃之象。无闇昧回谲之态。无偏僻倾危之行。显微无间。出处不殆。则上下之情志。自然有流通感应之妙。而身处乎康庄舒泰之地。美利施于国家。声名布于竹帛矣。贱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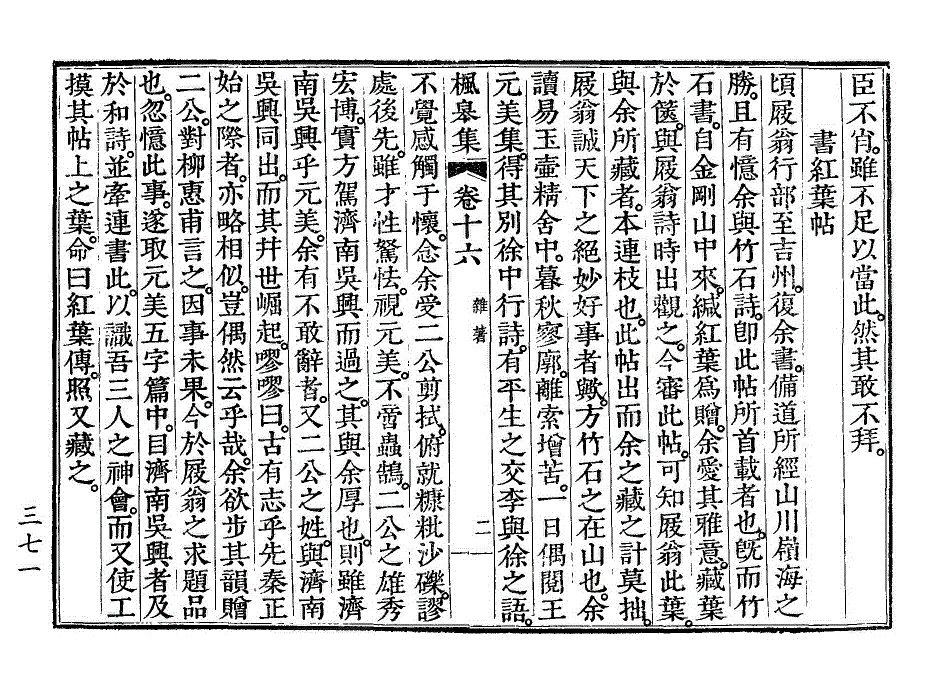 臣不肖。虽不足以当此。然其敢不拜。
臣不肖。虽不足以当此。然其敢不拜。书红叶帖
顷屐翁行部至吉州。复余书。备道所经山川岭海之胜。且有忆余与竹石诗。即此帖所首载者也。既而竹石书。自金刚山中来。缄红叶为赠。余爱其雅意。藏叶于箧。与屐翁诗时出观之。今审此帖。可知屐翁此叶。与余所藏者。本连枝也。此帖出而余之藏之计莫拙。屐翁诚天下之绝妙好事者欤。方竹石之在山也。余读易玉壶精舍中。暮秋寥廓。离索增苦。一日偶阅王元美集。得其别徐中行诗。有平生之交李与徐之语。不觉感触于怀。念余受二公剪拭。俯就糠秕沙砾。谬处后先。虽才性驽怯。视元美。不啻虫鹄。二公之雄秀宏博。实方驾济南吴兴而过之。其与余厚也。则虽济南吴兴乎元美。余有不敢辞者。又二公之姓。与济南吴兴同出。而其并世崛起。嘐嘐曰。古有志乎先秦正始之际者。亦略相似。岂偶然云乎哉。余欲步其韵赠二公。对柳惠甫言之。因事未果。今于屐翁之求题品也。忽忆此事。遂取元美五字篇中。目济南吴兴者及于和诗。并牵连书此。以识吾三人之神会。而又使工摸其帖上之叶。命曰红叶传。照又藏之。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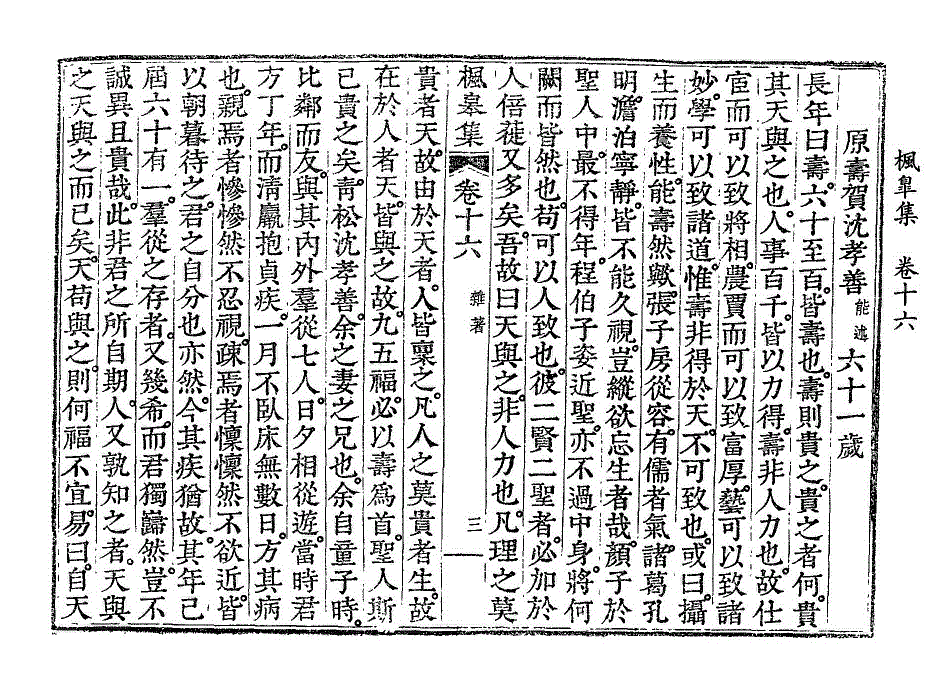 原寿贺沈孝善(能述)六十一岁
原寿贺沈孝善(能述)六十一岁长年曰寿。六十至百。皆寿也。寿则贵之。贵之者何。贵其天与之也。人事百千。皆以力得。寿非人力也。故仕宦而可以致将相。农贾而可以致富厚。艺可以致诸妙。学可以致诸道。惟寿非得于天。不可致也。或曰。摄生而养性。能寿然欤。张子房从容。有儒者气。诸葛孔明。澹泊宁静。皆不能久视。岂纵欲忘生者哉。颜子于圣人中。最不得年。程伯子姿近圣。亦不过中身。将何阙而皆然也。苟可以人致也。彼二贤二圣者。必加于人倍蓰又多矣。吾故曰天与之。非人力也。凡理之莫贵者天。故由于天者。人皆禀之。凡人之莫贵者生。故在于人者天。皆与之故。九五福。必以寿为首。圣人斯已贵之矣。青松沈孝善。余之妻之兄也。余自童子时。比邻而友。与其内外群从七人。日夕相从游。当时君方丁年。而清羸抱贞疾。一月不卧床无数日。方其病也。亲焉者惨惨然不忍视。疏焉者懔懔然不欲近。皆以朝暮待之。君之自分也亦然。今其疾犹故。其年已届六十有一。群从之存者。又几希。而君独岿然。岂不诚异且贵哉。此非君之所自期。人又孰知之者。天与之天与之而已矣。天苟与之。则何福不宜。易曰。自天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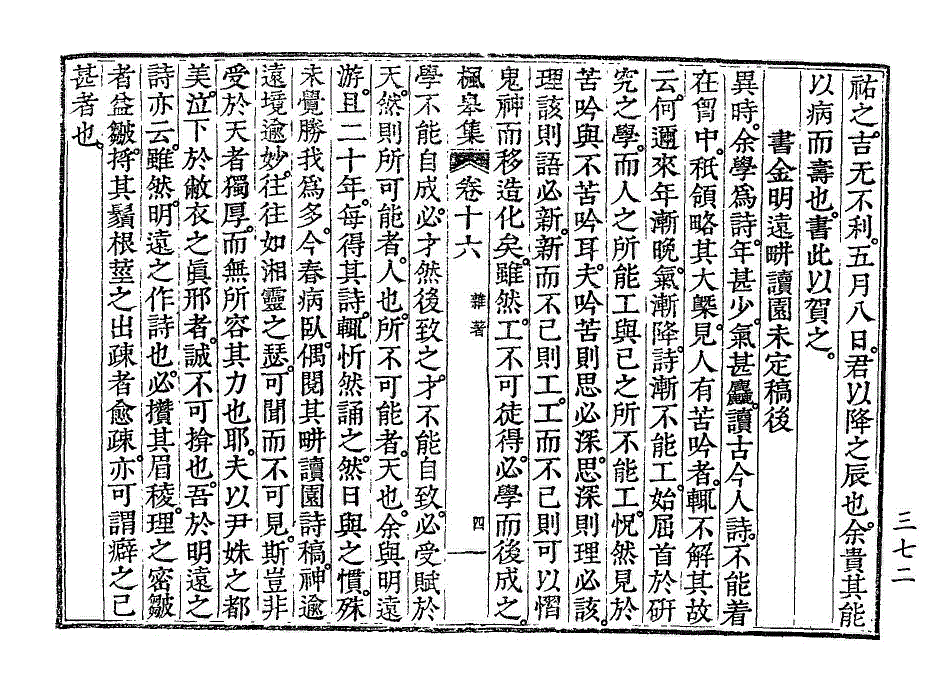 祐之。吉无不利。五月八日。君以降之辰也。余贵其能以病而寿也。书此以贺之。
祐之。吉无不利。五月八日。君以降之辰也。余贵其能以病而寿也。书此以贺之。书金明远耕读园未定稿后
异时。余学为诗。年甚少。气甚粗。读古今人诗。不能着在胸中。秖领略其大槩。见人有苦吟者。辄不解其故云。何迩来年渐晚。气渐降。诗渐不能工。始屈首于研究之学。而人之所能工与己之所不能工。恍然见于苦吟与不苦吟耳。夫吟苦则思必深。思深则理必该。理该则语必新。新而不已则工。工而不已则可以慑鬼神而移造化矣。虽然。工不可徒得。必学而后成之。学不能自成。必才然后致之。才不能自致。必受赋于天。然则所可能者。人也。所不可能者。天也。余与明远游。且二十年。每得其诗。辄忻然诵之。然日与之惯。殊未觉胜我为多。今春病卧。偶阅其耕读园诗稿。神逾远境逾妙。往往如湘灵之瑟。可闻而不可见。斯岂非受于天者独厚。而无所容其力也耶。夫以尹姝之都美。泣下于敝衣之真邢者。诚不可掩也。吾于明远之诗亦云。虽然。明远之作诗也。必攒其眉棱。理之密皱者益皱。捋其须根茎之出疏者愈疏。亦可谓癖之已甚者也。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3H 页
 书利原崔忠一所藏吾家故牍卷端
书利原崔忠一所藏吾家故牍卷端怨可忘乎。怨积者。不可不明也。德可弃乎。德虽小。不可遗也。小犹不可遗。况大者乎。在己犹不可遗。况在祖先乎。吾祖先累世。死王事。消长屈伸之际。怨与德。共半于世。为子孙者。痛念祖先之故。怨之必欲雪。德之必欲酬。即天理人情之宜也。然而其怨也公。故赖国家罔极之恩。稍雪其可雪者。而非子孙之所敢专也。惟德则止于私。故有当酬而力未之酬者。迄今六七十年。置之若相忘。盖势实然也。然则酬之当奈何。不过曰以心而已。今之为子孙者。苟能世世。以祖先之心为心。无事则殚诚而祛私。有事则拚身而循公以答国家之恩。祖先之灵。将悦豫于上曰。某不忘余心。余有孙。昔之施德于吾祖先者之灵。举必曰某有孙。不忝与有荣焉。如是则不期酬而酬之厚矣。不如是。虽日求其酬之之道。君子不与也。利原崔义士振暹之孙忠一。千里来见。且携示吾家故牍若干卷。请余志其端。以继世好。余为之书如此。盖义士当辛壬祸变时。施德于吾家甚大。事详三从叔吏议公所撰崔公碣文中。姑略之云。
风雨说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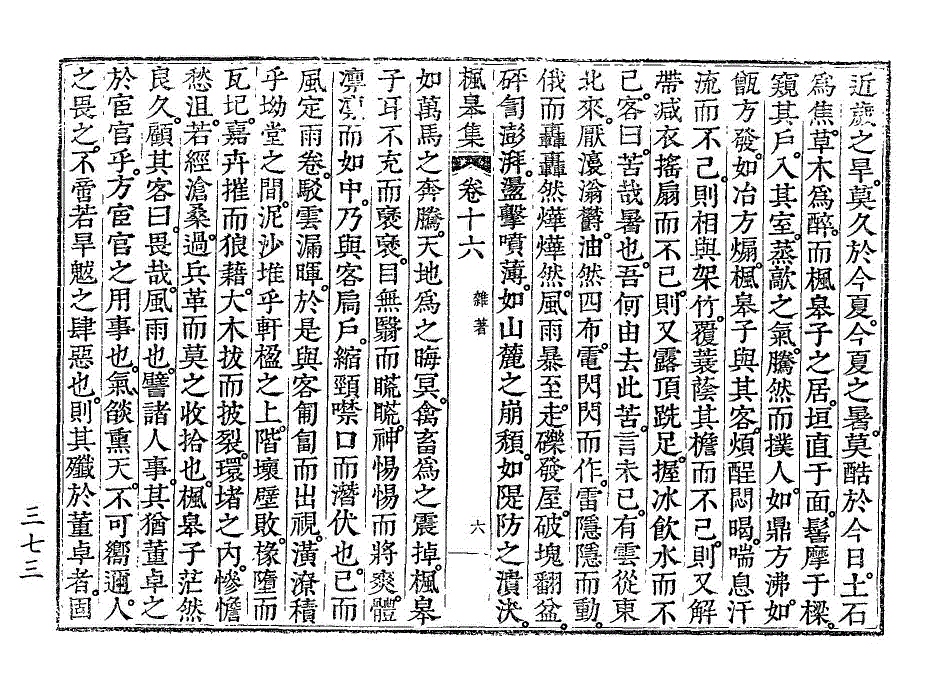 近岁之旱。莫久于今夏。今夏之暑。莫酷于今日。土石为焦。草木为醉。而枫皋子之居。垣直于面。髻摩于梁。窥其户。入其室。蒸歊之气。腾然而扑人。如鼎方沸。如甑方发。如冶方煽。枫皋子与其客。烦酲闷暍。喘息汗流而不已。则相与架竹。覆蓑荫其檐而不已。则又解带减衣摇扇而不已。则又露顶跣足。握冰饮水而不已。客曰。苦哉暑也。吾何由去此苦。言未已。有云从东北来。厌
近岁之旱。莫久于今夏。今夏之暑。莫酷于今日。土石为焦。草木为醉。而枫皋子之居。垣直于面。髻摩于梁。窥其户。入其室。蒸歊之气。腾然而扑人。如鼎方沸。如甑方发。如冶方煽。枫皋子与其客。烦酲闷暍。喘息汗流而不已。则相与架竹。覆蓑荫其檐而不已。则又解带减衣摇扇而不已。则又露顶跣足。握冰饮水而不已。客曰。苦哉暑也。吾何由去此苦。言未已。有云从东北来。厌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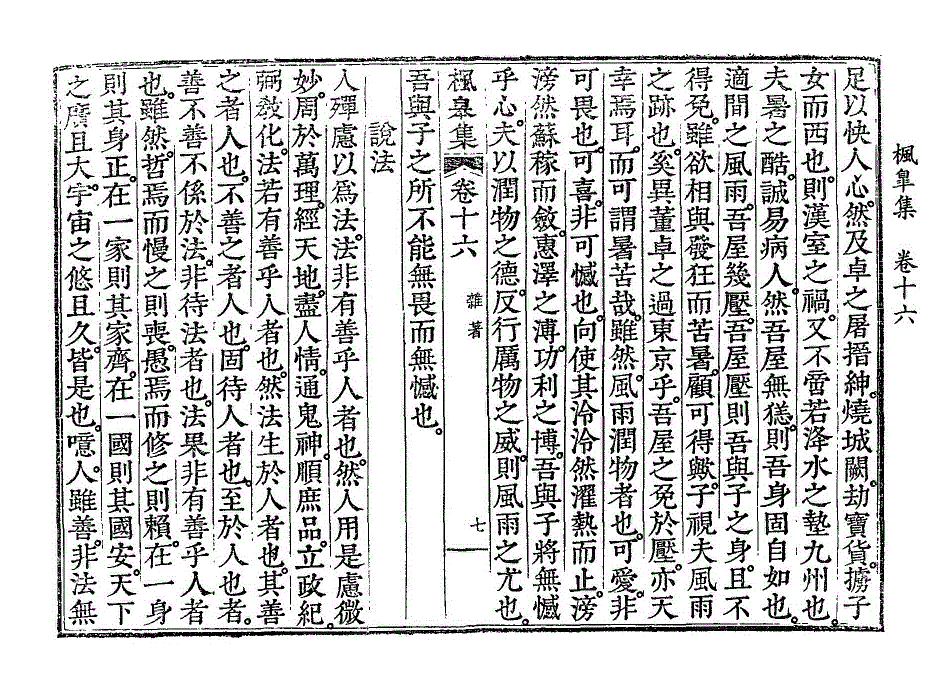 足以快人心。然及卓之屠搢绅。烧城阙。劫宝货。掳子女而西也。则汉室之祸。又不啻若洚水之垫九州也。夫暑之酷。诚易病人。然吾屋无㺊。则吾身固自如也。适间之风雨。吾屋几压。吾屋压则吾与子之身。且不得免。虽欲相与发狂而苦暑。顾可得欤。子视夫风雨之迹也。奚异董卓之过东京乎。吾屋之免于压。亦天幸焉耳。而可谓暑苦哉。虽然。风雨润物者也。可爱。非可畏也。可喜。非可憾也。向使其泠泠然濯热而止。滂滂然苏稼而敛。惠泽之溥。功利之博。吾与子将无憾乎心。夫以润物之德。反行厉物之威。则风雨之尤也。吾与子之所不能无畏而无憾也。
足以快人心。然及卓之屠搢绅。烧城阙。劫宝货。掳子女而西也。则汉室之祸。又不啻若洚水之垫九州也。夫暑之酷。诚易病人。然吾屋无㺊。则吾身固自如也。适间之风雨。吾屋几压。吾屋压则吾与子之身。且不得免。虽欲相与发狂而苦暑。顾可得欤。子视夫风雨之迹也。奚异董卓之过东京乎。吾屋之免于压。亦天幸焉耳。而可谓暑苦哉。虽然。风雨润物者也。可爱。非可畏也。可喜。非可憾也。向使其泠泠然濯热而止。滂滂然苏稼而敛。惠泽之溥。功利之博。吾与子将无憾乎心。夫以润物之德。反行厉物之威。则风雨之尤也。吾与子之所不能无畏而无憾也。说法
人殚虑以为法。法非有善乎人者也。然人用是虑微妙。周于万理。经天地。尽人情。通鬼神。顺庶品。立政纪。弼教化。法若有善乎人者也。然法生于人者也。其善之者人也。不善之者人也。固待人者也。至于人也者。善不善不系于法。非待法者也。法果非有善乎人者也。虽然。哲焉而慢之则丧。愚焉而修之则赖。在一身则其身正。在一家则其家齐。在一国则其国安。天下之广且大。宇宙之悠且久。皆是也。噫。人虽善。非法无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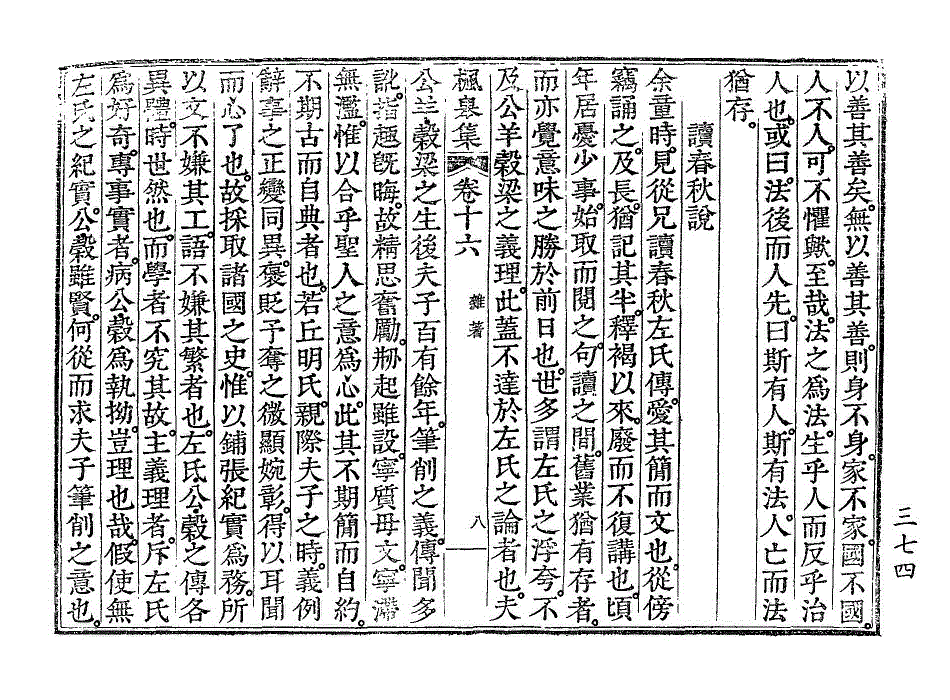 以善其善矣。无以善其善。则身不身。家不家。国不国。人不人。可不惧欤。至哉。法之为法。生乎人而反乎治人也。或曰。法后而人先。曰斯有人。斯有法。人亡而法犹存。
以善其善矣。无以善其善。则身不身。家不家。国不国。人不人。可不惧欤。至哉。法之为法。生乎人而反乎治人也。或曰。法后而人先。曰斯有人。斯有法。人亡而法犹存。读春秋说
余童时。见从兄读春秋左氏传。爱其简而文也。从傍窃诵之。及长。犹记其半。释褐以来。废而不复讲也。顷年居忧少事。始取而阅之。句读之间。旧业犹有存者。而亦觉意味之胜于前日也。世多谓左氏之浮夸。不及公羊谷梁之义理。此盖不达于左氏之论者也。夫公羊,谷梁之生后夫子百有馀年。笔削之义。传闻多讹。指趣既晦。故精思奋励。刱起虽设。宁质毋文。宁滞无滥。惟以合乎圣人之意为心。此其不期简而自约。不期古而自典者也。若丘明氏。亲际夫子之时。义例辞事之正变同异。褒贬予夺之微显婉彰。得以耳闻而心了也。故采取诸国之史。惟以铺张纪实为务。所以文不嫌其工。语不嫌其繁者也。左氏,公,谷之传各异体。时世然也。而学者不究其故。主义理者。斥左氏为好奇。专事实者。病公,谷为执拗。岂理也哉。假使无左氏之纪实。公,谷虽贤。何从而求夫子笔削之意也。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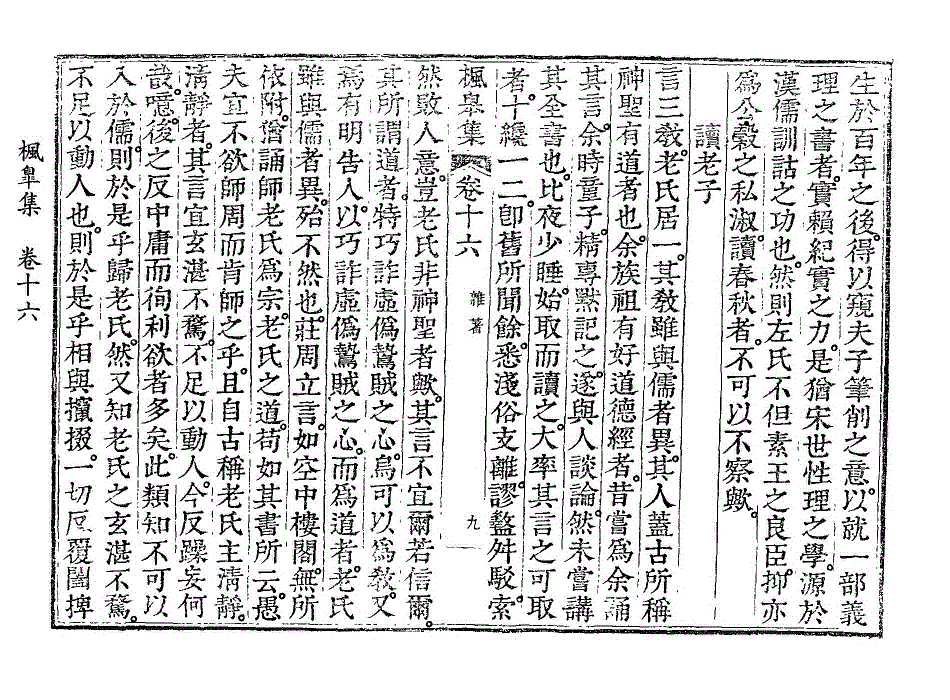 生于百年之后。得以窥夫子笔削之意。以就一部义理之书者。实赖纪实之力。是犹宋世性理之学。源于汉儒训诂之功也。然则左氏不但素王之良臣。抑亦为公,谷之私淑。读春秋者。不可以不察欤。
生于百年之后。得以窥夫子笔削之意。以就一部义理之书者。实赖纪实之力。是犹宋世性理之学。源于汉儒训诂之功也。然则左氏不但素王之良臣。抑亦为公,谷之私淑。读春秋者。不可以不察欤。读老子
言三教。老氏居一。其教虽与儒者异。其人盖古所称神圣有道者也。余族祖有好道德经者。昔尝为余诵其言。余时童子。精专默记之。遂与人谈论。然未尝讲其全书也。比夜少睡。始取而读之。大率其言之可取者。十才一二。即旧所闻馀。悉浅俗支离。谬盭舛驳。索然败人意。岂老氏非神圣者欤。其言不宜尔若信尔。其所谓道者。特巧诈虚伪鸷贼之心。乌可以为教。又焉有明告人。以巧诈虚伪鸷贼之心。而为道者。老氏虽与儒者异。殆不然也。庄周立言。如空中楼阁。无所依附。犹诵师老氏为宗。老氏之道。苟如其书所云。愚夫宜不欲师周而肯师之乎。且自古称老氏主清静。清静者。其言宜玄湛不骛。不足以动人。今反躁妄何哉。噫。后之反中庸而徇利欲者多矣。此类知不可以入于儒。则于是乎归老氏。然又知老氏之玄湛不骛。不足以动人也。则于是乎相与撺掇。一切反覆阖捭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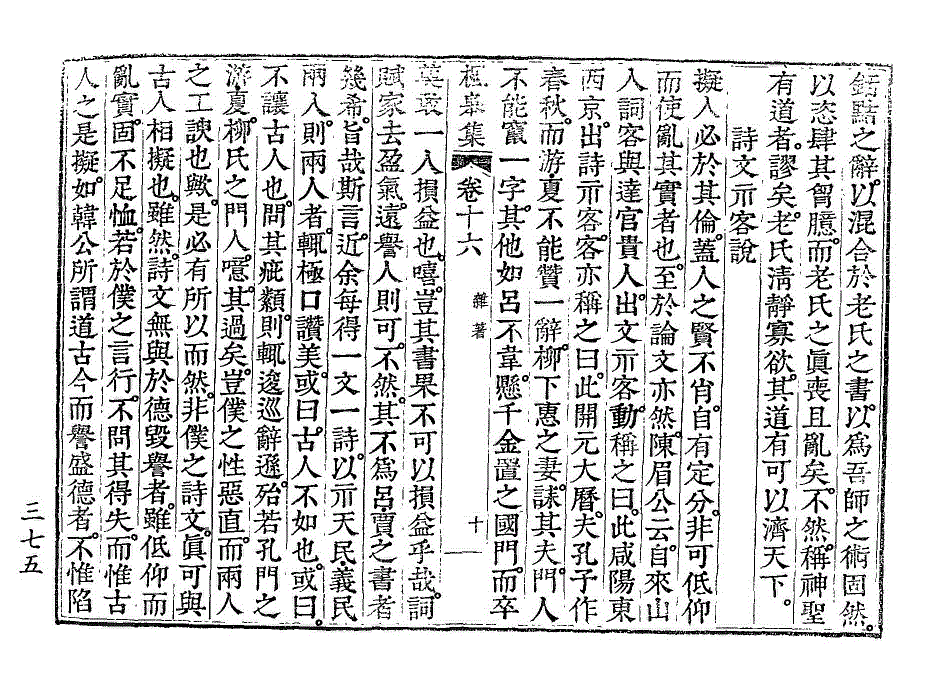 铦黠之辞。以混合于老氏之书。以为吾师之术固然。以恣肆其胸臆。而老氏之真丧且乱矣。不然。称神圣有道者。谬矣。老氏清静寡欲。其道有可以济天下。
铦黠之辞。以混合于老氏之书。以为吾师之术固然。以恣肆其胸臆。而老氏之真丧且乱矣。不然。称神圣有道者。谬矣。老氏清静寡欲。其道有可以济天下。诗文示客说
拟人必于其伦。盖人之贤不肖。自有定分。非可低仰而使乱其实者也。至于论文亦然。陈眉公云。自来山人词客与达官贵人。出文示客。动称之曰。此咸阳东西京。出诗示客。客亦称之曰。此开元大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赞一辞。柳下惠之妻。诔其夫。门人不能窜一字。其他如吕不韦。悬千金置之国门。而卒莫敢一人损益也。嘻。岂其书果不可以损益乎哉。词赋家去盈气。远誉人则可。不然。其不为吕,贾之书者几希。旨哉斯言。近余每得一文一诗。以示天民,义民两人。则两人者。辄极口赞美。或曰。古人不如也。或曰。不让古人也。问其疵颣。则辄逡巡辞逊。殆若孔门之游,夏。柳氏之门人。噫。其过矣。岂仆之性恶直。而两人之工谀也欤。是必有所以而然。非仆之诗文。真可与古人相拟也。虽然。诗文无与于德毁誉者。虽低仰而乱实。固不足恤。若于仆之言行。不问其得失。而惟古人之是拟。如韩公所谓道古今而誉盛德者。不惟陷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6H 页
 仆于不义。抑两人之自欺而欺人也。如是则两人之与仆交惟貌。而只视其巍巍也。非仆之所愿交于两人之心也。虽终身不复相见。何所恨焉。偶阅眉公语。书此以待两人之来。出示而质之。庸寓相勉之义。
仆于不义。抑两人之自欺而欺人也。如是则两人之与仆交惟貌。而只视其巍巍也。非仆之所愿交于两人之心也。虽终身不复相见。何所恨焉。偶阅眉公语。书此以待两人之来。出示而质之。庸寓相勉之义。书红流石刻诗后
世谓崔孤云作此诗。仆意不然。焉有仙人口气。浮露如此哉。必顽僧之粗解吟诗者。刻以欺世人。世人不悟。遂妄相沿袭。甚者谓非孤云不能作。噫。仙人而诗如彼。将焉用彼仙哉。
赠人
老杜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萧嵩荐之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穷谷一病叟耳。此东坡老人答贾耘老书也。不知老先生江居。可有如扁舟破浪之滕元发否。不然。箫公所谓帝王师穷谷病叟。岂非为先生传神耶。虽然。窃覵先生之意。内怀在山远志之实。外欲避急流勇退之名。求诸古人。惟陶隐居之山中宰相。髣髴似之。亦有岭上白云。不堪持赠也耶。陶公云虽不可以持赠。其于当世。大事未始不与闻而与论也。所居特山中耳。岂非所谓撄隐之名者哉。若是者。又不若安衣美食。行呼唱于道路者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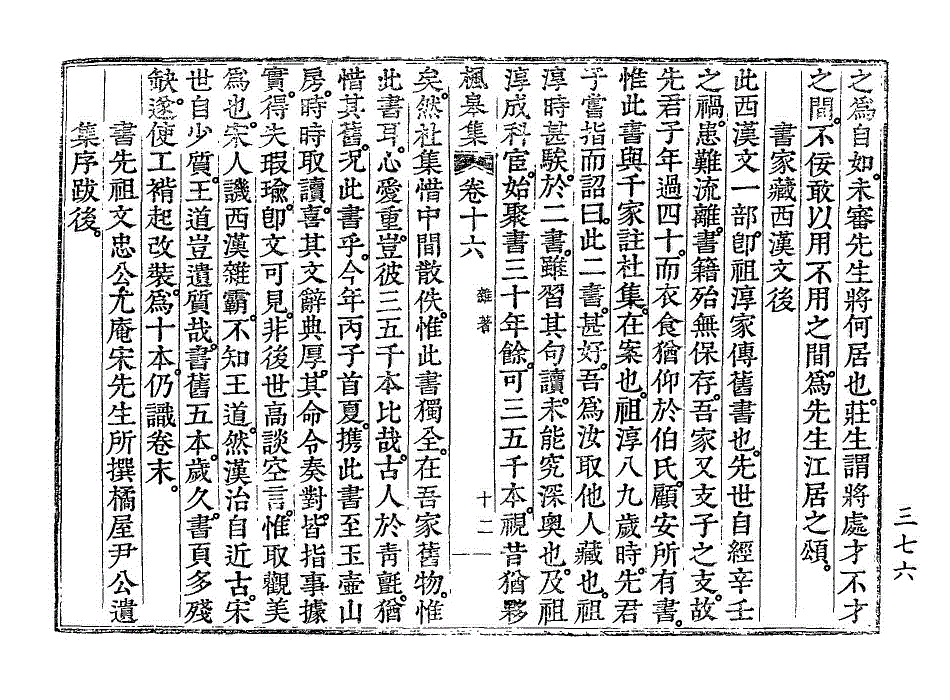 之为自如。未审先生将何居也。庄生谓将处才不才之间。不佞敢以用不用之间。为先生江居之颂。
之为自如。未审先生将何居也。庄生谓将处才不才之间。不佞敢以用不用之间。为先生江居之颂。书家藏西汉文后
此西汉文一部。即祖淳家传旧书也。先世自经辛壬之祸。患难流离。书籍殆无保存。吾家又支子之支。故先君子年过四十。而衣食犹仰于伯氏。顾安所有书。惟此书与千家注杜集。在案也。祖淳八九岁时。先君子尝指而诏曰。此二书。甚好。吾为汝取他人藏也。祖淳时甚騃。于二书。虽习其句读。未能究深奥也。及祖淳成科宦。始聚书三十年馀。可三五千本。视昔犹夥矣。然杜集惜中间散佚。惟此书独全。在吾家旧物。惟此书耳。心爱重。岂彼三五千本比哉。古人于青毡。犹惜其旧。况此书乎。今年丙子首夏。携此书至玉壶山房。时时取读。喜其文辞典厚。其命令奏对。皆指事据实。得失瑕瑜。即文可见。非后世高谈空言。惟取观美为也。宋人讥西汉杂霸。不知王道。然汉治自近古。宋世自少质。王道岂遗质哉。书旧五本。岁久。书页多残缺。遂使工褙起改装。为十本。仍识卷末。
书先祖文忠公,尤庵宋先生所撰橘屋尹公遗集序跋后。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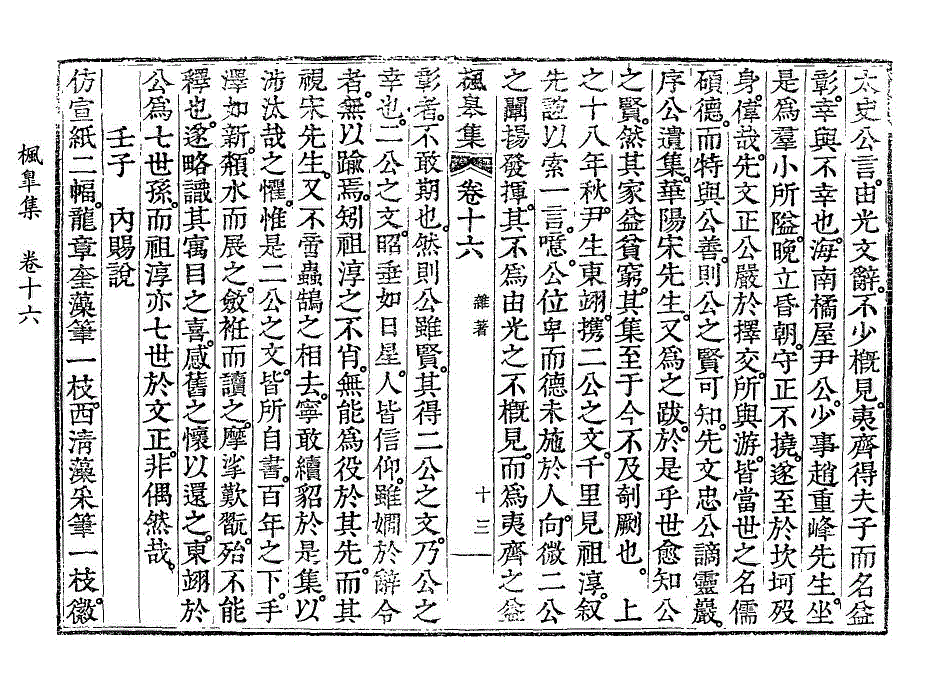 太史公言。由光文辞。不少概见。夷,齐得夫子而名益彰。幸与不幸也。海南橘屋尹公。少事赵重峰先生。坐是为群小所隘。晚立昏朝。守正不挠。遂至于坎坷殁身。伟哉。先文正公严于择交。所与游。皆当世之名儒硕德。而特与公善。则公之贤可知。先文忠公谪灵岩。序公遗集。华阳宋先生。又为之跋。于是乎世愈知公之贤。然其家益贫穷。其集至于今不及剞劂也。 上之十八年秋。尹生东翊。携二公之文。千里见祖淳。叙先谊以索一言。噫。公位卑而德未施于人。向微二公之阐扬发挥。其不为由光之不概见。而为夷,齐之益彰者。不敢期也。然则公虽贤。其得二公之文。乃公之幸也。二公之文。昭垂如日星。人皆信仰。虽娴于辞令者。无以踰焉。矧祖淳之不肖。无能为役于其先。而其视宋先生。又不啻虫鹄之相去。宁敢续貂于是集。以涉汰哉之惧。惟是二公之文。皆所自书。百年之下。手泽如新。颒水而展之。敛衽而读之。摩挲叹玩。殆不能释也。遂略识其寓目之喜。感旧之怀以还之。东翊于公为七世孙。而祖淳亦七世于文正。非偶然哉。
太史公言。由光文辞。不少概见。夷,齐得夫子而名益彰。幸与不幸也。海南橘屋尹公。少事赵重峰先生。坐是为群小所隘。晚立昏朝。守正不挠。遂至于坎坷殁身。伟哉。先文正公严于择交。所与游。皆当世之名儒硕德。而特与公善。则公之贤可知。先文忠公谪灵岩。序公遗集。华阳宋先生。又为之跋。于是乎世愈知公之贤。然其家益贫穷。其集至于今不及剞劂也。 上之十八年秋。尹生东翊。携二公之文。千里见祖淳。叙先谊以索一言。噫。公位卑而德未施于人。向微二公之阐扬发挥。其不为由光之不概见。而为夷,齐之益彰者。不敢期也。然则公虽贤。其得二公之文。乃公之幸也。二公之文。昭垂如日星。人皆信仰。虽娴于辞令者。无以踰焉。矧祖淳之不肖。无能为役于其先。而其视宋先生。又不啻虫鹄之相去。宁敢续貂于是集。以涉汰哉之惧。惟是二公之文。皆所自书。百年之下。手泽如新。颒水而展之。敛衽而读之。摩挲叹玩。殆不能释也。遂略识其寓目之喜。感旧之怀以还之。东翊于公为七世孙。而祖淳亦七世于文正。非偶然哉。壬子 内赐说
仿宣纸二幅。龙章奎藻笔一枝。西清藻采笔一枝。徽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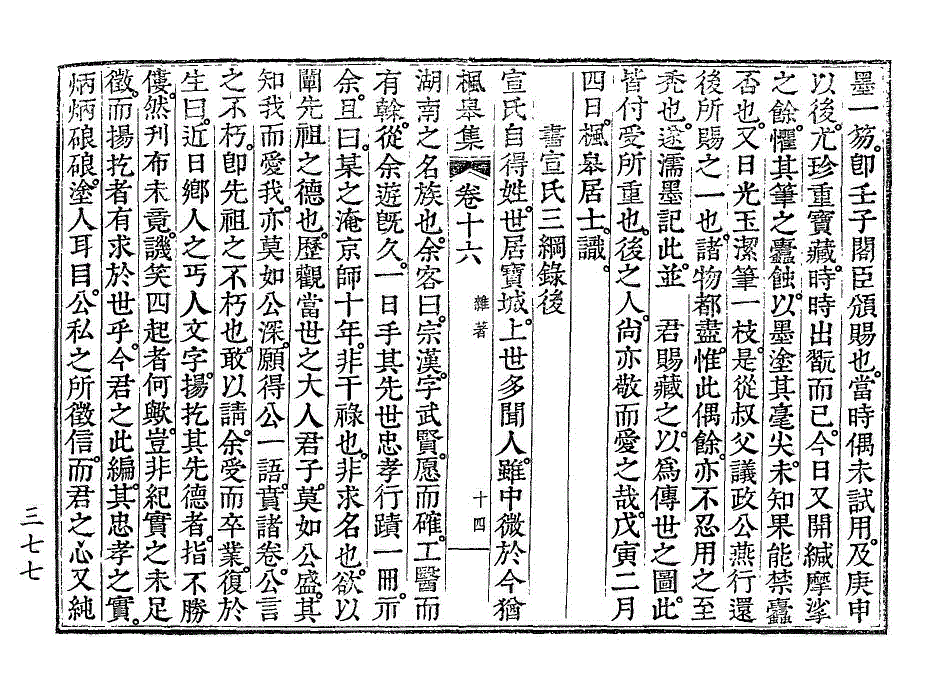 墨一笏。即壬子阁臣颁赐也。当时偶未试用。及庚申以后。尤珍重宝藏。时时出玩而已。今日又开缄摩挲之馀。惧其笔之蠹蚀。以墨涂其毫尖。未知果能禁蠹否也。又日光玉洁笔一枝。是从叔父议政公燕行还后所赐之一也。诸物都尽。惟此偶馀。亦不忍用之至秃也。途濡墨记此。并 君赐藏之。以为传世之图。此皆付受所重也。后之人。尚亦敬而爱之哉。戊寅二月四日。枫皋居士。识。
墨一笏。即壬子阁臣颁赐也。当时偶未试用。及庚申以后。尤珍重宝藏。时时出玩而已。今日又开缄摩挲之馀。惧其笔之蠹蚀。以墨涂其毫尖。未知果能禁蠹否也。又日光玉洁笔一枝。是从叔父议政公燕行还后所赐之一也。诸物都尽。惟此偶馀。亦不忍用之至秃也。途濡墨记此。并 君赐藏之。以为传世之图。此皆付受所重也。后之人。尚亦敬而爱之哉。戊寅二月四日。枫皋居士。识。书宣氏三纲录后
宣氏自得姓。世居宝城。上世多闻人。虽中微于今犹湖南之名族也。余客曰。宗汉。字武贤。愿而确。工医而有干。从余游既久。一日手其先世忠孝行迹一册。示余。且曰。某之淹京师十年。非干禄也。非求名也。欲以阐先祖之德也。历观当世之大人君子。莫如公盛。其知我而爱我。亦莫如公深。愿得公一语。贲诸卷。公言之不朽。即先祖之不朽也。敢以请。余受而卒业。复于生曰。近日乡人之丐人文字。扬扢其先德者。指不胜偻。然刊布未竟。讥笑四起者何欤。岂非纪实之未足徵。而扬扢者有求于世乎。今君之此编。其忠孝之实。炳炳硠硠。涂人耳目。公私之所徵信。而君之心又纯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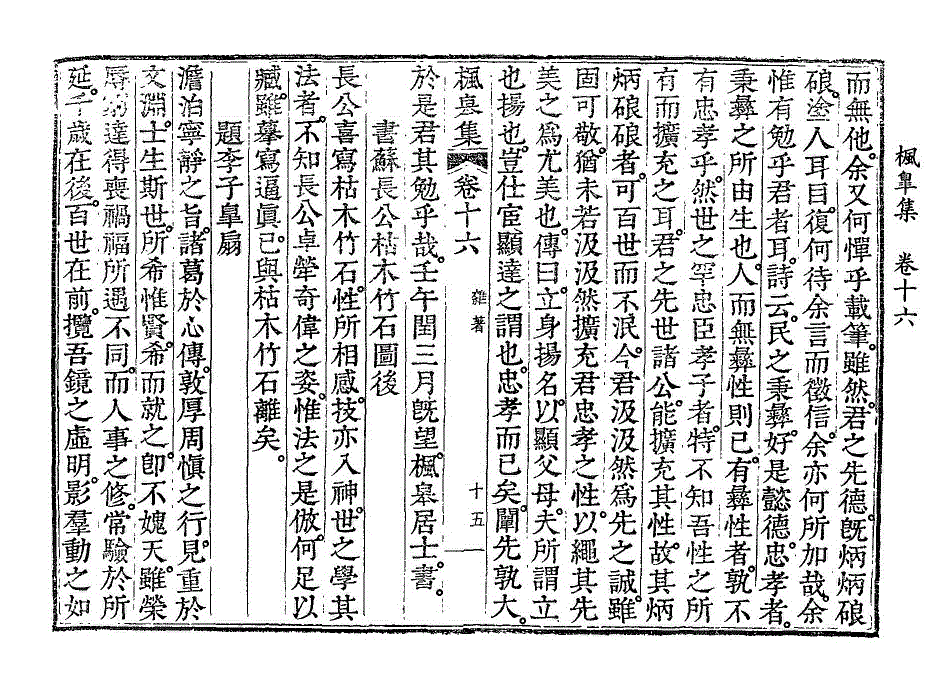 而无他。余又何惮乎载笔。虽然。君之先德。既炳炳硠硠。涂人耳目。复何待余言而徵信。余亦何所加哉。余惟有勉乎君者耳。诗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忠孝者。秉彝之所由生也。人而无彝性则已。有彝性者。孰不有忠孝乎。然世之罕忠臣孝子者。特不知吾性之所有而扩充之耳。君之先世诸公。能扩充其性。故其炳炳硠硠者。可百世而不泯。今君汲汲然为先之诚。虽固可敬。犹未若汲汲然扩充君忠孝之性。以绳其先美之为尤美也。传曰。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夫所谓立也扬也。岂仕宦显达之谓也。忠孝而已矣。阐先孰大。于是君其勉乎哉。壬午闰三月既望。枫皋居士。书。
而无他。余又何惮乎载笔。虽然。君之先德。既炳炳硠硠。涂人耳目。复何待余言而徵信。余亦何所加哉。余惟有勉乎君者耳。诗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忠孝者。秉彝之所由生也。人而无彝性则已。有彝性者。孰不有忠孝乎。然世之罕忠臣孝子者。特不知吾性之所有而扩充之耳。君之先世诸公。能扩充其性。故其炳炳硠硠者。可百世而不泯。今君汲汲然为先之诚。虽固可敬。犹未若汲汲然扩充君忠孝之性。以绳其先美之为尤美也。传曰。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夫所谓立也扬也。岂仕宦显达之谓也。忠孝而已矣。阐先孰大。于是君其勉乎哉。壬午闰三月既望。枫皋居士。书。书苏长公枯木竹石图后
长公喜写枯木竹石。性所相感。技亦入神。世之学其法者。不知长公卓荦奇伟之姿。惟法之是仿。何足以臧。虽摹写逼真。已与枯木竹石离矣。
题李子皋扇
澹泊宁静之旨。诸葛于心传。敦厚周慎之行。见重于文渊。士生斯世。所希惟贤。希而就之。即不愧天。虽荣辱穷达得丧祸福所遇不同。而人事之修。常验于所延。千岁在后。百世在前。揽吾镜之虚明。影群动之如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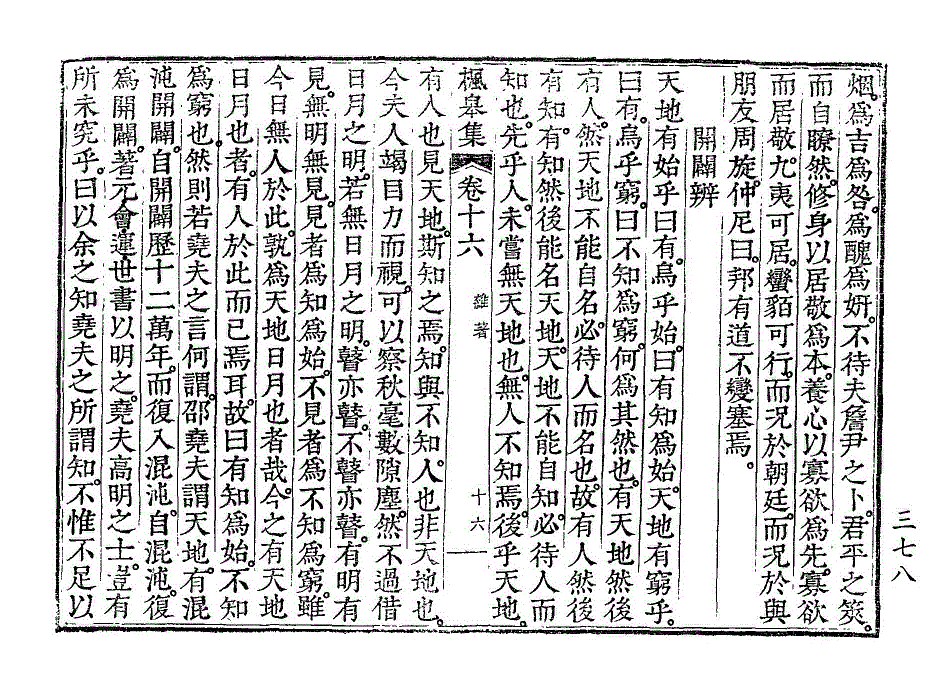 烟。为吉为咎。为丑为妍。不待夫詹尹之卜。君平之筴。而自瞭然。修身以居敬为本。养心以寡欲为先。寡欲而居敬。九夷可居。蛮貊可行。而况于朝廷。而况于与朋友周旋。仲尼曰。邦有道不变塞焉。
烟。为吉为咎。为丑为妍。不待夫詹尹之卜。君平之筴。而自瞭然。修身以居敬为本。养心以寡欲为先。寡欲而居敬。九夷可居。蛮貊可行。而况于朝廷。而况于与朋友周旋。仲尼曰。邦有道不变塞焉。开辟辨
天地有始乎。曰有。乌乎始。曰有知为始。天地有穷乎。曰有。乌乎穷。曰不知为穷。何为其然也。有天地然后有人。然天地不能自名。必待人而名也。故有人然后有知。有知然后能名天地。天地不能自知。必待人而知也。先乎人。未尝无天地也。无人不知焉。后乎天地。有人也见天地。斯知之焉。知与不知。人也非天地也。今夫人竭目力而视。可以察秋毫数隙尘。然不过借日月之明。若无日月之明。瞽亦瞽。不瞽亦瞽。有明有见。无明无见。见者为知为始。不见者为不知为穷。虽今日无人于此。孰为天地日月也者哉。今之有天地日月也者。有人于此而已焉耳。故曰有知为始。不知为穷也。然则若尧夫之言何谓。邵尧夫谓天地。有混沌开辟。自开辟历十二万年。而复入混沌。自混沌。复为开辟。著元,会,运,世书以明之。尧夫高明之士。岂有所未究乎。曰以余之知尧夫之所谓知。不惟不足以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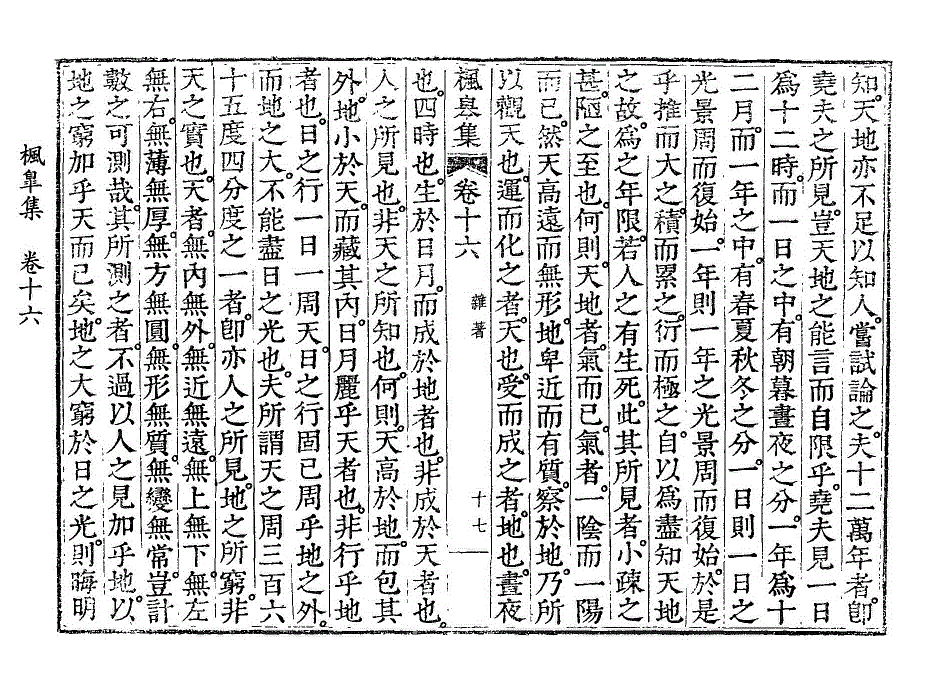 知。天地亦不足以知人。尝试论之。夫十二万年者。即尧夫之所见。岂天地之能言而自限乎。尧夫见一日为十二时。而一日之中。有朝暮昼夜之分。一年为十二月。而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日则一日之光景周而复始。一年则一年之光景周而复始。于是乎推而大之。积而累之。衍而极之。自以为尽知天地之故。为之年限。若人之有生死。此其所见者。小疏之甚。陋之至也。何则。天地者。气而已。气者。一阴而一阳而已。然天高远而无形。地卑近而有质。察于地。乃所以观天也。运而化之者。天也。受而成之者。地也。昼夜也。四时也。生于日月。而成于地者也。非成于天者也。人之所见也。非天之所知也。何则。天高于地。而包其外。地小于天。而藏其内。日月丽乎天者也。非行乎地者也。日之行一日一周天。日之行固已周乎地之外。而地之大。不能尽日之光也。夫所谓天之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即亦人之所见。地之所穷。非天之实也。天者。无内无外。无近无远。无上无下。无左无右。无薄无厚。无方无圆。无形无质。无变无常。岂计数之可测哉。其所测之者。不过以人之见加乎地。以地之穷加乎天而已矣。地之大穷于日之光。则晦明
知。天地亦不足以知人。尝试论之。夫十二万年者。即尧夫之所见。岂天地之能言而自限乎。尧夫见一日为十二时。而一日之中。有朝暮昼夜之分。一年为十二月。而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日则一日之光景周而复始。一年则一年之光景周而复始。于是乎推而大之。积而累之。衍而极之。自以为尽知天地之故。为之年限。若人之有生死。此其所见者。小疏之甚。陋之至也。何则。天地者。气而已。气者。一阴而一阳而已。然天高远而无形。地卑近而有质。察于地。乃所以观天也。运而化之者。天也。受而成之者。地也。昼夜也。四时也。生于日月。而成于地者也。非成于天者也。人之所见也。非天之所知也。何则。天高于地。而包其外。地小于天。而藏其内。日月丽乎天者也。非行乎地者也。日之行一日一周天。日之行固已周乎地之外。而地之大。不能尽日之光也。夫所谓天之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即亦人之所见。地之所穷。非天之实也。天者。无内无外。无近无远。无上无下。无左无右。无薄无厚。无方无圆。无形无质。无变无常。岂计数之可测哉。其所测之者。不过以人之见加乎地。以地之穷加乎天而已矣。地之大穷于日之光。则晦明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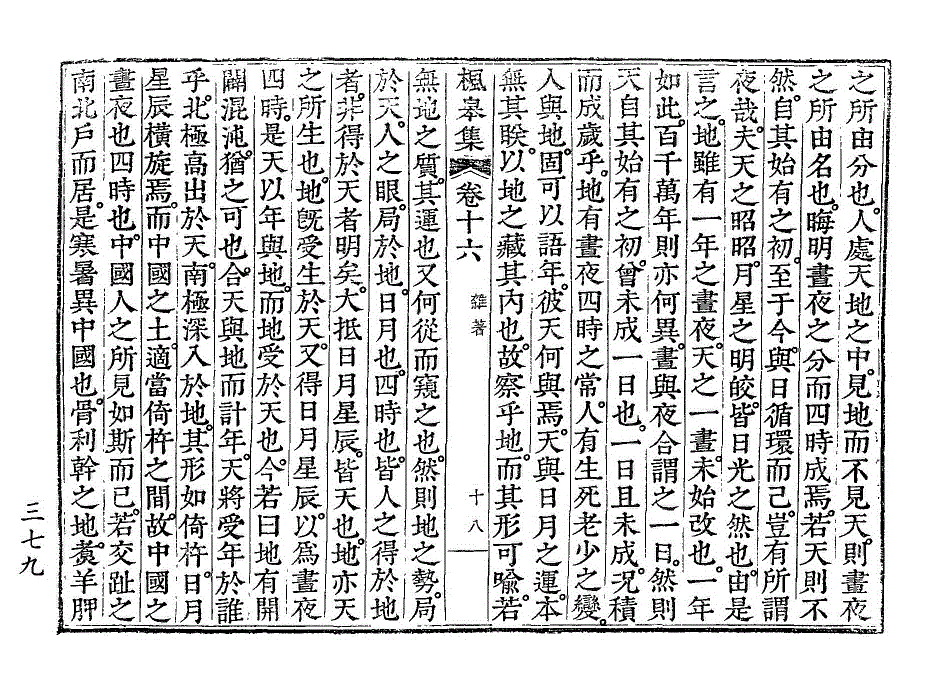 之所由分也。人处天地之中。见地而不见天。则昼夜之所由名也。晦明昼夜之分而四时成焉。若天则不然。自其始有之初。至于今。与日循环而已。岂有所谓夜哉。夫天之昭昭。月星之明皎。皆日光之然也。由是言之。地虽有一年之昼夜。天之一昼。未始改也。一年如此。百千万年则亦何异。昼与夜合谓之一日。然则天自其始有之初。曾未成一日也。一日且未成。况积而成岁乎。地有昼夜四时之常。人有生死老少之变。人与地。固可以语年。彼天何与焉。天与日月之运。本无其眹。以地之藏其内也。故察乎地。而其形可喻。若无地之质。其运也又何从而窥之也。然则地之势。局于天。人之眼。局于地。日月也。四时也。皆人之得于地者。非得于天者明矣。大抵日月星辰。皆天也。地亦天之所生也。地既受生于天。又得日月星辰。以为昼夜四时。是天以年与地。而地受于天也。今若曰地有开辟混沌。犹之可也。合天与地而计年。天将受年于谁乎。北极高出于天。南极深入于地。其形如倚杵。日月星辰横旋焉。而中国之土。适当倚杵之间。故中国之昼夜也四时也。中国人之所见如斯而已。若交趾之南北户而居。是寒暑异中国也。骨利干之地。煮羊胛
之所由分也。人处天地之中。见地而不见天。则昼夜之所由名也。晦明昼夜之分而四时成焉。若天则不然。自其始有之初。至于今。与日循环而已。岂有所谓夜哉。夫天之昭昭。月星之明皎。皆日光之然也。由是言之。地虽有一年之昼夜。天之一昼。未始改也。一年如此。百千万年则亦何异。昼与夜合谓之一日。然则天自其始有之初。曾未成一日也。一日且未成。况积而成岁乎。地有昼夜四时之常。人有生死老少之变。人与地。固可以语年。彼天何与焉。天与日月之运。本无其眹。以地之藏其内也。故察乎地。而其形可喻。若无地之质。其运也又何从而窥之也。然则地之势。局于天。人之眼。局于地。日月也。四时也。皆人之得于地者。非得于天者明矣。大抵日月星辰。皆天也。地亦天之所生也。地既受生于天。又得日月星辰。以为昼夜四时。是天以年与地。而地受于天也。今若曰地有开辟混沌。犹之可也。合天与地而计年。天将受年于谁乎。北极高出于天。南极深入于地。其形如倚杵。日月星辰横旋焉。而中国之土。适当倚杵之间。故中国之昼夜也四时也。中国人之所见如斯而已。若交趾之南北户而居。是寒暑异中国也。骨利干之地。煮羊胛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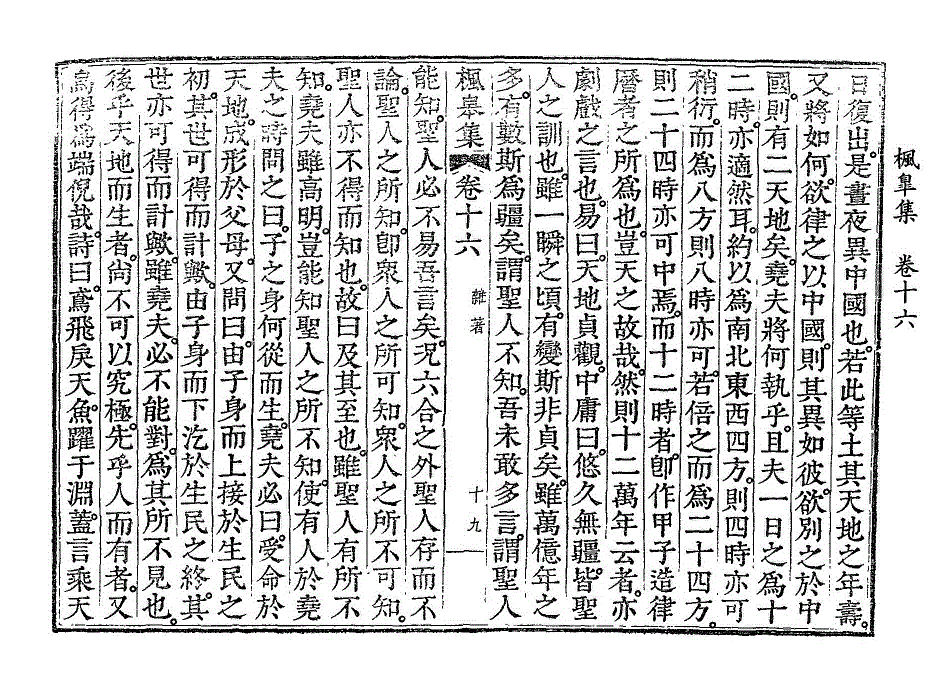 日复出。是昼夜异中国也。若此等土其天地之年寿。又将如何。欲律之以中国。则其异如彼。欲别之于中国。则有二天地矣。尧夫将何执乎。且夫一日之为十二时。亦适然耳。约以为南北东西四方。则四时亦可稍衍。而为八方则八时亦可。若倍之而为二十四方。则二十四时亦可中焉。而十二时者。即作甲子造律历者之所为也。岂天之故哉。然则十二万年云者。亦剧戏之言也。易曰。天地贞观。中庸曰。悠久无疆。皆圣人之训也。虽一瞬之顷。有变斯非贞矣。虽万亿年之多。有数斯为疆矣。谓圣人不知。吾未敢多言。谓圣人能知。圣人必不易吾言矣。况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圣人之所知。即众人之所可知。众人之所不可知。圣人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尧夫虽高明。岂能知圣人之所不知。使有人于尧夫之时问之曰。子之身何从而生。尧夫必曰。受命于天地。成形于父母。又问曰。由子身而上接于生民之初。其世可得而计欤。由子身而下汔于生民之终。其世亦可得而计欤。虽尧夫。必不能对。为其所不见也。后乎天地而生者。尚不可以究极。先乎人而有者。又乌得为端倪哉。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盖言乘天
日复出。是昼夜异中国也。若此等土其天地之年寿。又将如何。欲律之以中国。则其异如彼。欲别之于中国。则有二天地矣。尧夫将何执乎。且夫一日之为十二时。亦适然耳。约以为南北东西四方。则四时亦可稍衍。而为八方则八时亦可。若倍之而为二十四方。则二十四时亦可中焉。而十二时者。即作甲子造律历者之所为也。岂天之故哉。然则十二万年云者。亦剧戏之言也。易曰。天地贞观。中庸曰。悠久无疆。皆圣人之训也。虽一瞬之顷。有变斯非贞矣。虽万亿年之多。有数斯为疆矣。谓圣人不知。吾未敢多言。谓圣人能知。圣人必不易吾言矣。况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圣人之所知。即众人之所可知。众人之所不可知。圣人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尧夫虽高明。岂能知圣人之所不知。使有人于尧夫之时问之曰。子之身何从而生。尧夫必曰。受命于天地。成形于父母。又问曰。由子身而上接于生民之初。其世可得而计欤。由子身而下汔于生民之终。其世亦可得而计欤。虽尧夫。必不能对。为其所不见也。后乎天地而生者。尚不可以究极。先乎人而有者。又乌得为端倪哉。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盖言乘天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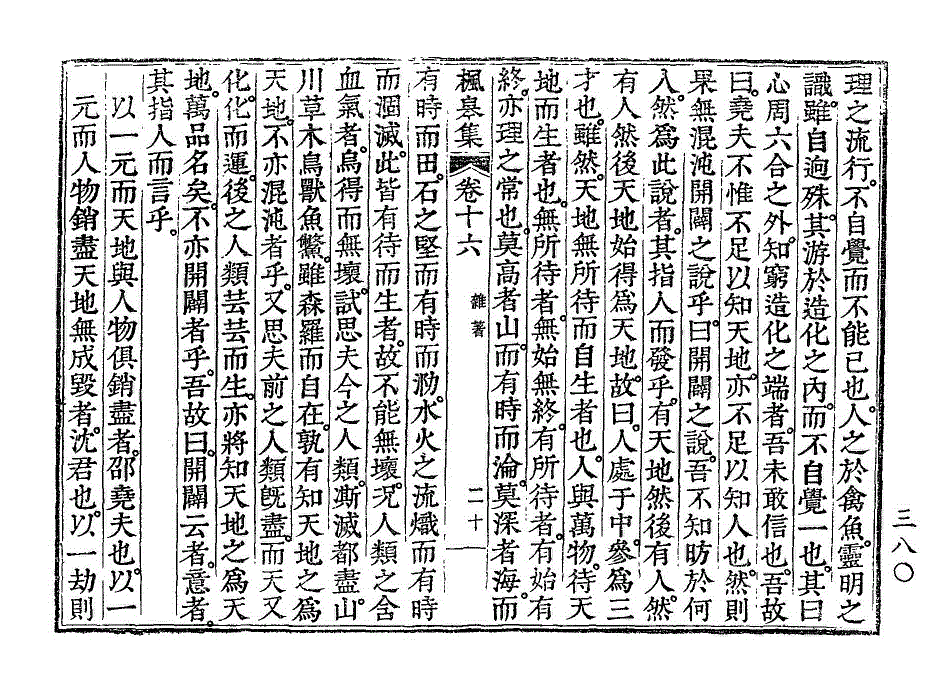 理之流行。不自觉而不能已也。人之于禽鱼。灵明之识。虽自迥殊。其游于造化之内。而不自觉一也。其曰心周六合之外。知穷造化之端者。吾未敢信也。吾故曰。尧夫不惟不足以知天地。亦不足以知人也。然则果无混沌开辟之说乎。曰开辟之说。吾不知昉于何人。然为此说者。其指人而发乎。有天地然后有人。然有人然后天地始得为天地。故曰。人处于中。参为三才也。虽然。天地无所待而自生者也。人与万物。待天地而生者也。无所待者。无始无终。有所待者。有始有终。亦理之常也。莫高者山。而有时而沦。莫深者海。而有时而田。石之坚而有时而泐。水火之流炽而有时而涸灭。此皆有待而生者。故不能无坏。况人类之含血气者。乌得而无坏。试思夫今之人类。凘灭都尽。山川草木鸟兽鱼鳖。虽森罗而自在。孰有知天地之为天地。不亦混沌者乎。又思夫前之人类既尽。而天又化。化而运。后之人类芸芸而生。亦将知天地之为天地。万品名矣。不亦开辟者乎。吾故曰。开辟云者。意者。其指人而言乎。
理之流行。不自觉而不能已也。人之于禽鱼。灵明之识。虽自迥殊。其游于造化之内。而不自觉一也。其曰心周六合之外。知穷造化之端者。吾未敢信也。吾故曰。尧夫不惟不足以知天地。亦不足以知人也。然则果无混沌开辟之说乎。曰开辟之说。吾不知昉于何人。然为此说者。其指人而发乎。有天地然后有人。然有人然后天地始得为天地。故曰。人处于中。参为三才也。虽然。天地无所待而自生者也。人与万物。待天地而生者也。无所待者。无始无终。有所待者。有始有终。亦理之常也。莫高者山。而有时而沦。莫深者海。而有时而田。石之坚而有时而泐。水火之流炽而有时而涸灭。此皆有待而生者。故不能无坏。况人类之含血气者。乌得而无坏。试思夫今之人类。凘灭都尽。山川草木鸟兽鱼鳖。虽森罗而自在。孰有知天地之为天地。不亦混沌者乎。又思夫前之人类既尽。而天又化。化而运。后之人类芸芸而生。亦将知天地之为天地。万品名矣。不亦开辟者乎。吾故曰。开辟云者。意者。其指人而言乎。以一元而天地与人物俱销尽者。邵尧夫也。以一元而人物销尽天地无成毁者。沈君也。以一劫则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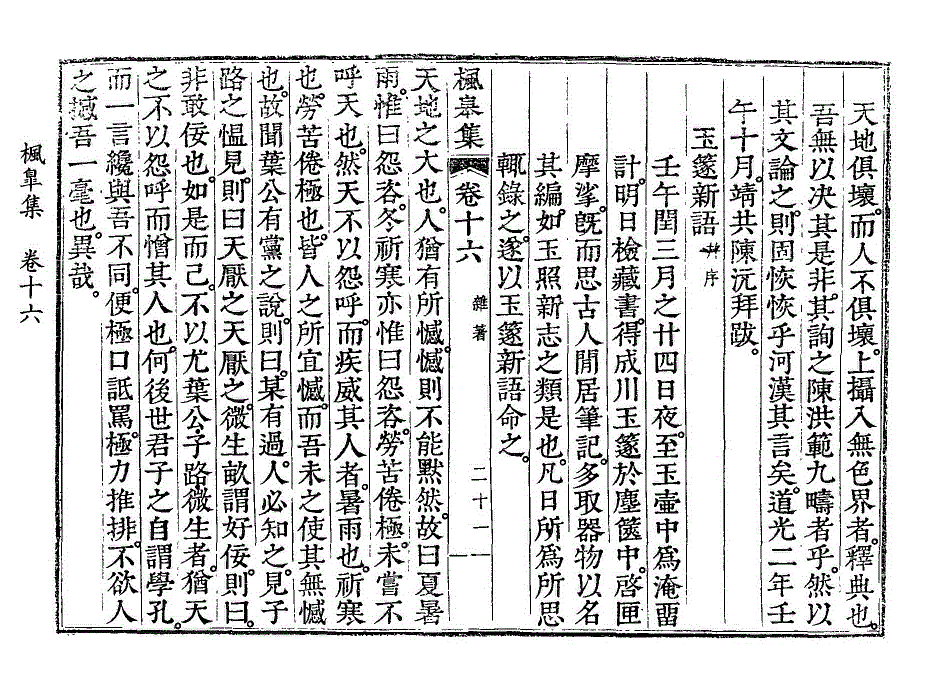 天地俱坏。而人不俱坏。上摄入无色界者。释典也。吾无以决其是非。其询之陈洪范九畴者乎。然以其文论之。则固恢恢乎河汉其言矣。道光二年壬午十月。靖共陈沅拜跋。
天地俱坏。而人不俱坏。上摄入无色界者。释典也。吾无以决其是非。其询之陈洪范九畴者乎。然以其文论之。则固恢恢乎河汉其言矣。道光二年壬午十月。靖共陈沅拜跋。玉篴新语(并序)
壬午闰三月之廿四日夜。至玉壶中为淹留计。明日检藏书。得成川玉篴于尘箧中。启匣摩挲。既而思古人閒居笔记。多取器物以名其编。如玉照新志之类是也。凡日所为所思辄录之。遂以玉篴新语命之。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憾则不能默然。故曰夏暑雨。惟曰怨咨。冬祈寒亦惟曰怨咨。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然天不以怨呼。而疾威其人者。暑雨也。祈寒也。劳苦倦极也。皆人之所宜憾。而吾未之使其无憾也。故闻叶公有党之说。则曰。某有过。人必知之。见子路之愠见。则曰天厌之天厌之。微生亩谓好佞。则曰。非敢佞也。如是而已。不以尤叶公,子路,微生者。犹天之不以怨呼而憎其人也。何后世君子之自谓学孔。而一言才与吾不同。便极口诋骂。极力推排。不欲人之撼吾一毫也。异哉。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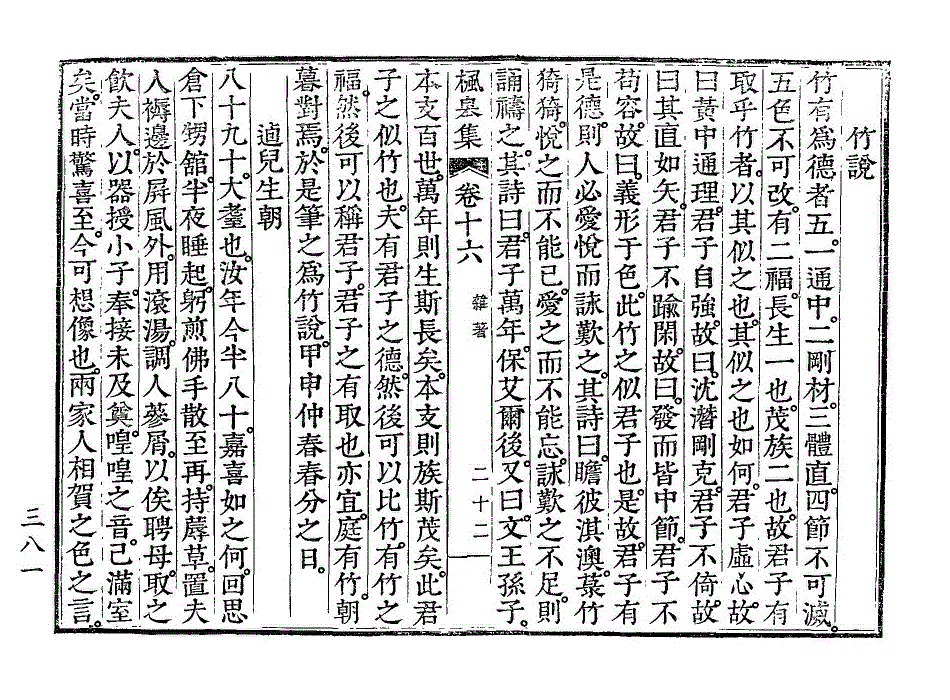 竹说
竹说竹有为德者五。一通中。二刚材。三体直。四节不可灭。五色不可改。有二福。长生一也。茂族二也。故君子有取乎竹者。以其似之也。其似之也如何。君子虚心。故曰黄中通理。君子自强。故曰。沈潜刚克。君子不倚。故曰其直如矢。君子不踰闲。故曰。发而皆中节。君子不苟容。故曰。义形于色。此竹之似君子也。是故。君子有是德。则人必爱悦而咏叹之。其诗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悦之而不能已。爱之而不能忘。咏叹之不足。则诵祷之。其诗曰。君子万年。保艾尔后。又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万年则生斯长矣。本支则族斯茂矣。此君子之似竹也。夫有君子之德。然后可以比竹。有竹之福。然后可以称君子。君子之有取也亦宜。庭有竹。朝暮对焉。于是笔之为竹说。甲申仲春春分之日。
逌儿生朝
八十九十。大耋也。汝年今半八十。嘉喜如之何。回思仓下甥馆。半夜睡起。躬煎佛手散至再。持蓐草。置夫人褥边于屏风外。用滚汤。调人蔘屑。以俟聘母。取之饮夫人。以器授小子。奉接未及奠。喤喤之音。已满室矣。当时惊喜至。今可想像也。两家人相贺之色之言。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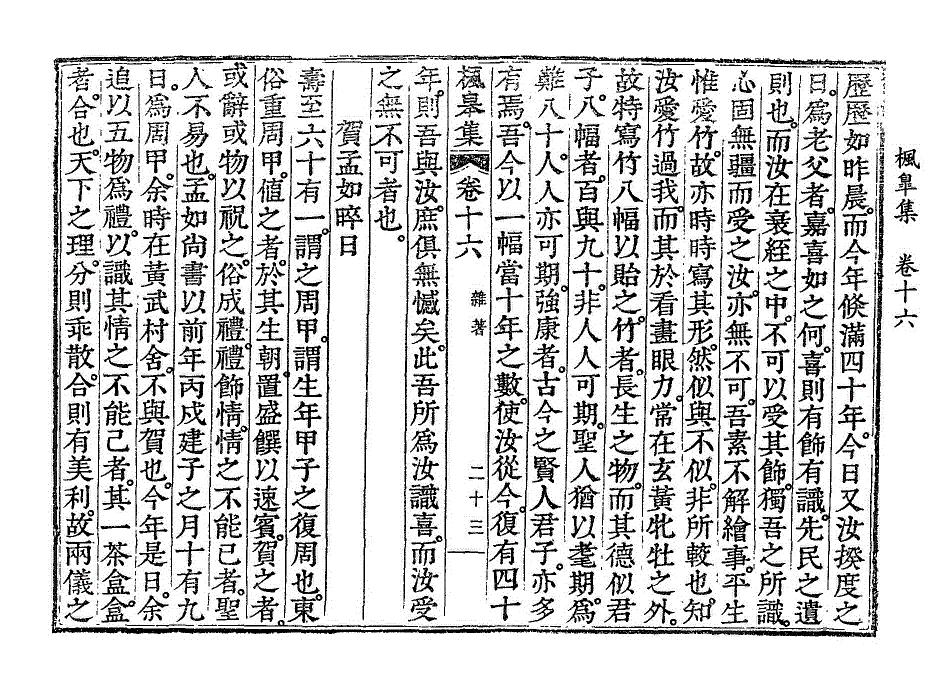 历历如昨晨。而今年倏满四十年。今日又汝揆度之日。为老父者。嘉喜如之何。喜则有饰有识。先民之遗则也。而汝在衰绖之中。不可以受其饰。独吾之所识。心固无疆而受之汝。亦无不可。吾素不解绘事。平生惟爱竹。故亦时时写其形。然似与不似。非所较也。知汝爱竹过我。而其于看画眼力。常在玄黄牝牡之外。故特写竹八幅以贻之。竹者。长生之物。而其德似君子。八幅者。百与九十。非人人可期。圣人犹以耄期。为难八十。人人亦可期。强康者。古今之贤人君子。亦多有焉。吾今以一幅当十年之数。使汝从今。复有四十年。则吾与汝。庶俱无憾矣。此吾所为汝识喜。而汝受之无不可者也。
历历如昨晨。而今年倏满四十年。今日又汝揆度之日。为老父者。嘉喜如之何。喜则有饰有识。先民之遗则也。而汝在衰绖之中。不可以受其饰。独吾之所识。心固无疆而受之汝。亦无不可。吾素不解绘事。平生惟爱竹。故亦时时写其形。然似与不似。非所较也。知汝爱竹过我。而其于看画眼力。常在玄黄牝牡之外。故特写竹八幅以贻之。竹者。长生之物。而其德似君子。八幅者。百与九十。非人人可期。圣人犹以耄期。为难八十。人人亦可期。强康者。古今之贤人君子。亦多有焉。吾今以一幅当十年之数。使汝从今。复有四十年。则吾与汝。庶俱无憾矣。此吾所为汝识喜。而汝受之无不可者也。贺孟如晬日
寿至六十有一。谓之周甲。谓生年甲子之复周也。东俗重周甲。值之者。于其生朝。置盛馔以速宾。贺之者。或辞或物以祝之。俗成礼。礼饰情。情之不能已者。圣人不易也。孟如尚书以前年丙戌建子之月十有九日。为周甲。余时在黄武村舍。不与贺也。今年是日。余追以五物为礼。以识其情之不能已者。其一茶盒。盒者。合也。天下之理。分则乖散。合则有美利。故两仪之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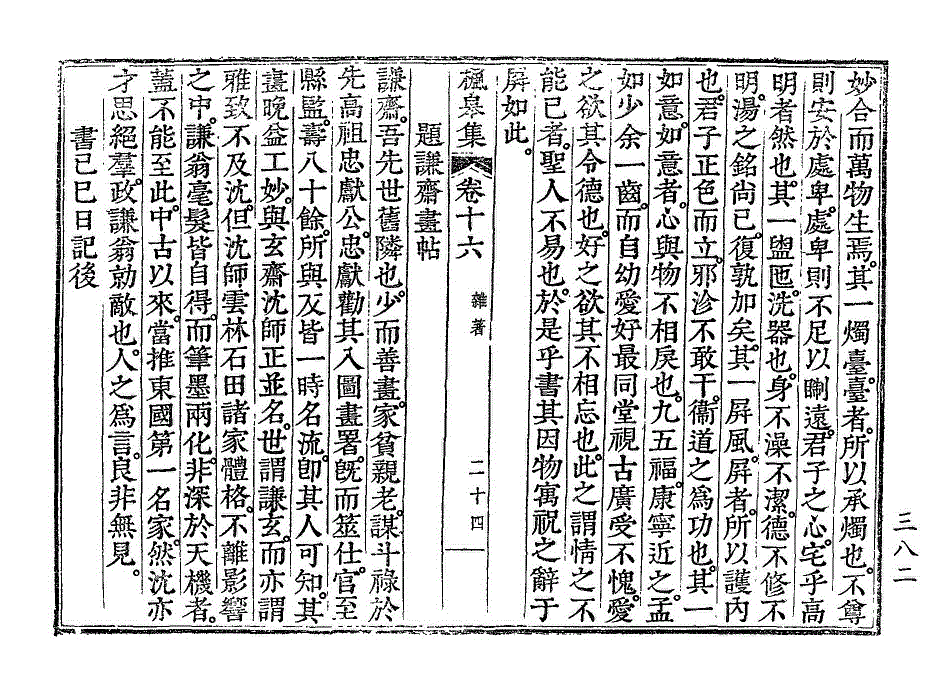 妙合而万物生焉。其一烛台。台者。所以承烛也。不尊则安于处卑。处卑则不足以晢远。君子之心。宅乎高明者然也。其一盥匜。洗器也。身不澡不洁。德不修不明。汤之铭尚已。复孰加矣。其一屏风。屏者。所以护内也。君子正色而立。邪沴不敢干。卫道之为功也。其一如意。如意者。心与物不相戾也。九五福。康宁近之。孟如少余一齿。而自幼爱好最同堂视古广受不愧。爱之欲其令德也。好之欲其不相忘也。此之谓情之不能已者。圣人不易也。于是乎书其因物寓祝之辞于屏如此。
妙合而万物生焉。其一烛台。台者。所以承烛也。不尊则安于处卑。处卑则不足以晢远。君子之心。宅乎高明者然也。其一盥匜。洗器也。身不澡不洁。德不修不明。汤之铭尚已。复孰加矣。其一屏风。屏者。所以护内也。君子正色而立。邪沴不敢干。卫道之为功也。其一如意。如意者。心与物不相戾也。九五福。康宁近之。孟如少余一齿。而自幼爱好最同堂视古广受不愧。爱之欲其令德也。好之欲其不相忘也。此之谓情之不能已者。圣人不易也。于是乎书其因物寓祝之辞于屏如此。题谦斋画帖
谦斋。吾先世旧邻也。少而善画。家贫亲老。谋斗禄于先高祖忠献公。忠献劝其入图画署。既而筮仕。官至县监。寿八十馀。所与友皆一时名流。即其人可知。其画晚益工妙。与玄斋沈师正并名。世谓谦,玄。而亦谓雅致不及沈。但沈师云林石田诸家体格。不离影响之中。谦翁毫发皆自得。而笔墨两化。非深于天机者。盖不能至此。中古以来。当推东国第一名家。然沈亦才思绝群。政谦翁勍敌也。人之为言。良非无见。
书己巳日记后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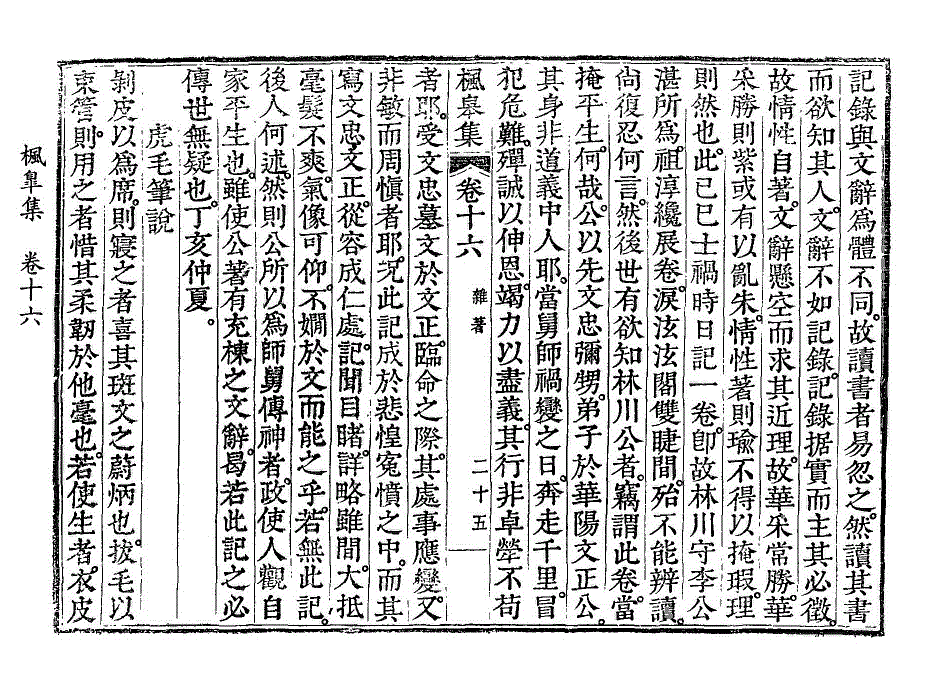 记录与文辞为体不同。故读书者易忽之。然读其书而欲知其人。文辞不如记录。记录据实而主其必徵。故情性自著。文辞悬空而求其近理。故华采常胜。华采胜则紫或有以乱朱。情性著则瑜不得以掩瑕。理则然也。此己巳士祸时日记一卷。即故林川守李公湛所为。祖淳才展卷。泪泫泫阁双睫间。殆不能辨读。尚复忍何言。然后世有欲知林川公者。窃谓此卷。当掩平生。何哉。公以先文忠弥甥。弟子于华阳文正公。其身非道义中人耶。当舅师祸变之日。奔走千里。冒犯危难。殚诚以伸恩。竭力以尽义。其行非卓荦不苟者耶。受文忠墓文于文正。临命之际。其处事应变。又非敏而周慎者耶。况此记成于悲惶冤愤之中。而其写文忠,文正。从容成仁处。记闻目睹。详略虽间。大抵毫发不爽。气像可仰。不娴于文而能之乎。若无此记。后人何述。然则公所以为师舅传神者。政使人观自家平生也。虽使公著有充栋之文辞。曷若此记之必传世无疑也。丁亥仲夏。
记录与文辞为体不同。故读书者易忽之。然读其书而欲知其人。文辞不如记录。记录据实而主其必徵。故情性自著。文辞悬空而求其近理。故华采常胜。华采胜则紫或有以乱朱。情性著则瑜不得以掩瑕。理则然也。此己巳士祸时日记一卷。即故林川守李公湛所为。祖淳才展卷。泪泫泫阁双睫间。殆不能辨读。尚复忍何言。然后世有欲知林川公者。窃谓此卷。当掩平生。何哉。公以先文忠弥甥。弟子于华阳文正公。其身非道义中人耶。当舅师祸变之日。奔走千里。冒犯危难。殚诚以伸恩。竭力以尽义。其行非卓荦不苟者耶。受文忠墓文于文正。临命之际。其处事应变。又非敏而周慎者耶。况此记成于悲惶冤愤之中。而其写文忠,文正。从容成仁处。记闻目睹。详略虽间。大抵毫发不爽。气像可仰。不娴于文而能之乎。若无此记。后人何述。然则公所以为师舅传神者。政使人观自家平生也。虽使公著有充栋之文辞。曷若此记之必传世无疑也。丁亥仲夏。虎毛笔说
剥皮以为席。则寝之者喜其斑文之蔚炳也。拔毛以束管。则用之者惜其柔韧于他毫也。若使生者。衣皮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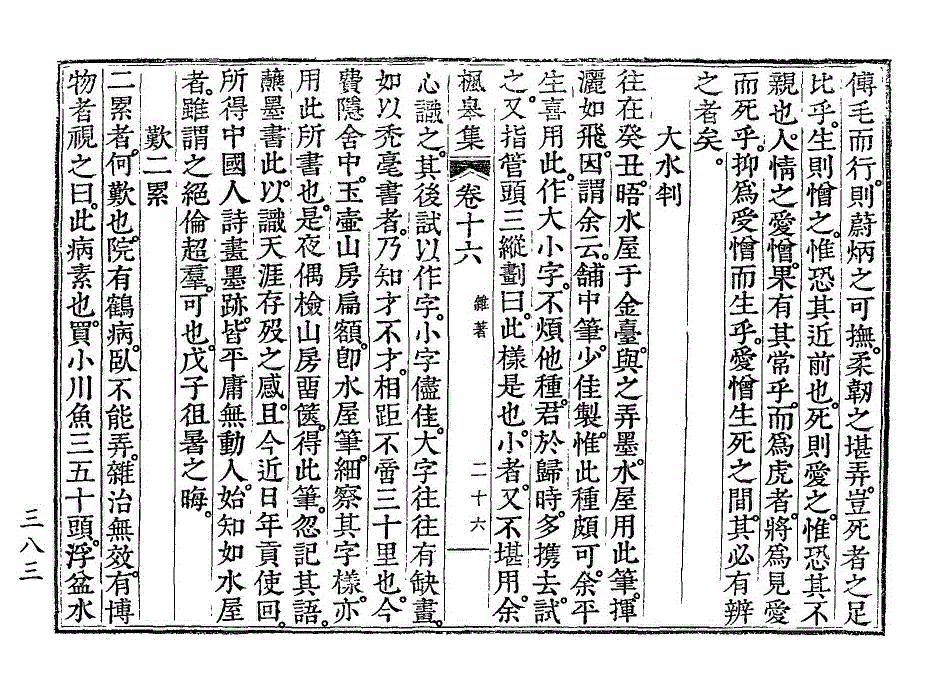 傅毛而行。则蔚炳之可抚。柔韧之堪弄。岂死者之足比乎。生则憎之。惟恐其近前也。死则爱之。惟恐其不亲也。人情之爱憎。果有其常乎。而为虎者。将为见爱而死乎。抑为受憎而生乎。爱憎生死之间。其必有辨之者矣。
傅毛而行。则蔚炳之可抚。柔韧之堪弄。岂死者之足比乎。生则憎之。惟恐其近前也。死则爱之。惟恐其不亲也。人情之爱憎。果有其常乎。而为虎者。将为见爱而死乎。抑为受憎而生乎。爱憎生死之间。其必有辨之者矣。大水判
往在癸丑。晤水屋于金台。与之弄墨。水屋用此笔。挥洒如飞。因谓余云。铺中笔。少佳制。惟此种颇可。余平生喜用此。作大小字。不烦他种。君于归时。多携去。试之。又指管头三纵划曰。此样是也。小者。又不堪用。余心识之。其后试以作字。小字尽佳。大字往往有缺画。如以秃毫书者。乃知才不才。相距不啻三十里也。今费隐舍中。玉壶山房扁额。即水屋笔。细察其字样。亦用此所书也。是夜偶检山房留箧。得此笔。忽记其语。蘸墨书此。以识天涯存殁之感。且今近日年贡使回。所得中国人诗画墨迹。皆平庸无动人。始知如水屋者。虽谓之绝伦超群。可也。戊子徂暑之晦。
叹二累
二累者。何叹也。院有鹤病。卧不能弄。杂治无效。有博物者视之曰。此病素也。买小川鱼三五十头。浮盆水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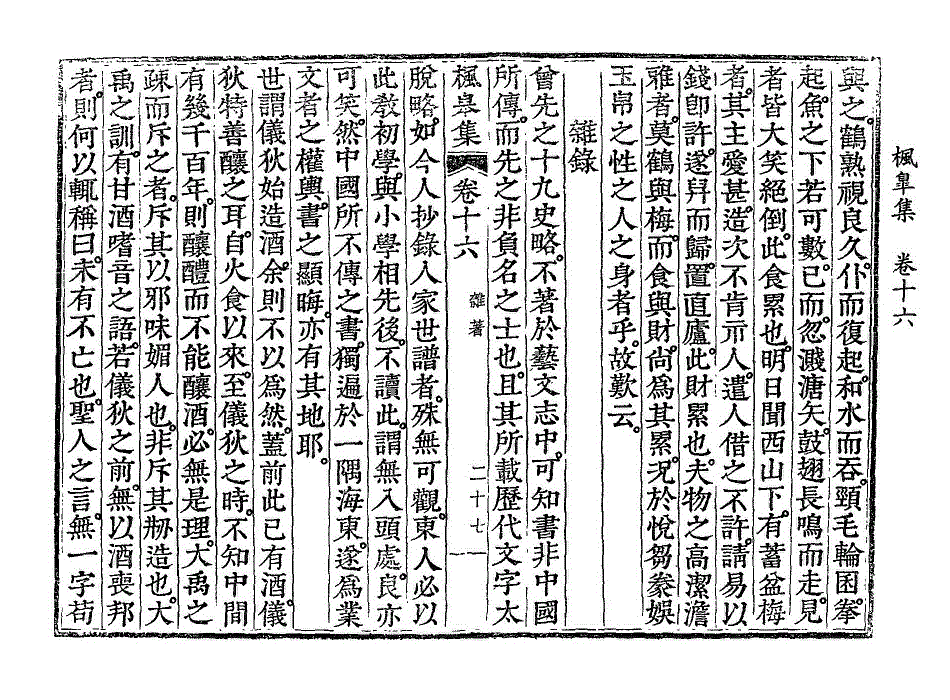 与之。鹤熟视良久。仆而复起。和水而吞。颈毛轮囷。拳起。鱼之下若可数。已而。忽溅溏矢。鼓翅长鸣而走。见者皆大笑绝倒。此食累也。明日闻西山下。有蓄盆梅者。其主爱甚。造次不肯示人。遣人借之不许。请易以钱即许。遂舁而归。置直庐。此财累也。夫物之高洁澹雅者。莫鹤与梅。而食与财。尚为其累。况于悦刍豢娱玉帛之性之人之身者乎。故叹云。
与之。鹤熟视良久。仆而复起。和水而吞。颈毛轮囷。拳起。鱼之下若可数。已而。忽溅溏矢。鼓翅长鸣而走。见者皆大笑绝倒。此食累也。明日闻西山下。有蓄盆梅者。其主爱甚。造次不肯示人。遣人借之不许。请易以钱即许。遂舁而归。置直庐。此财累也。夫物之高洁澹雅者。莫鹤与梅。而食与财。尚为其累。况于悦刍豢娱玉帛之性之人之身者乎。故叹云。杂录
曾先之十九史略。不著于艺文志中。可知书非中国所传。而先之非负名之士也。且其所载历代文字太脱略。如今人抄录人家世谱者。殊无可观。东人必以此教初学。与小学相先后。不读此。谓无入头处。良亦可笑。然中国所不传之书。独遍于一隅海东。遂为业文者之权舆。书之显晦。亦有其地耶。
世谓仪狄始造酒。余则不以为然。盖前此已有酒。仪狄特善酿之耳。自火食以来。至仪狄之时。不知中间有几千百年。则酿醴而不能酿酒。必无是理。大禹之疏而斥之者。斥其以邪味媚人也。非斥其刱造也。大禹之训。有甘酒嗜音之语。若仪狄之前。无以酒丧邦者。则何以辄称曰。未有不亡也。圣人之言。无一字苟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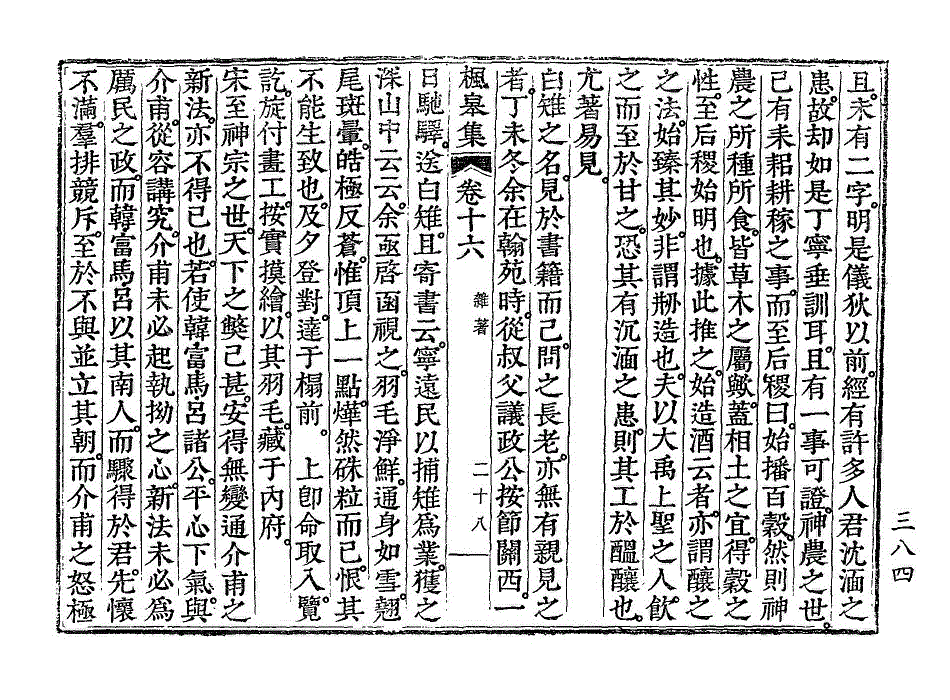 且。未有二字。明是仪狄以前。经有许多人君沈湎之患。故却如是丁宁垂训耳。且有一事可證。神农之世。已有耒耜耕稼之事。而至后稷曰。始播百谷。然则神农之所种所食。皆草木之属欤。盖相土之宜。得谷之性。至后稷始明也。据此推之。始造酒云者。亦谓酿之之法。始臻其妙。非谓刱造也。夫以大禹上圣之人。饮之而至于甘之。恐其有沉湎之患。则其工于酝酿也。尤著易见。
且。未有二字。明是仪狄以前。经有许多人君沈湎之患。故却如是丁宁垂训耳。且有一事可證。神农之世。已有耒耜耕稼之事。而至后稷曰。始播百谷。然则神农之所种所食。皆草木之属欤。盖相土之宜。得谷之性。至后稷始明也。据此推之。始造酒云者。亦谓酿之之法。始臻其妙。非谓刱造也。夫以大禹上圣之人。饮之而至于甘之。恐其有沉湎之患。则其工于酝酿也。尤著易见。白雉之名。见于书籍而已。问之长老。亦无有亲见之者。丁未冬余在翰苑时。从叔父议政公按节关西。一日驰驿。送白雉。且寄书云。宁远民以捕雉为业。获之深山中云云。余亟启函视之。羽毛净鲜。通身如雪。翘尾斑晕。皓极反苍。惟顶上一点。烨然朱粒而已。恨其不能生致也。及夕登对。达于榻前。 上即命取入。览讫。旋付画工。按实摸绘。以其羽毛。藏于内府。
宋至神宗之世。天下之弊已甚。安得无变通介甫之新法。亦不得已也。若使韩,富,马,吕诸公。平心下气。与介甫。从容讲究。介甫未必起执拗之心。新法未必为厉民之政。而韩,富,马,吕以其南人。而骤得于君。先怀不满。群排竞斥。至于不与并立其朝。而介甫之怒极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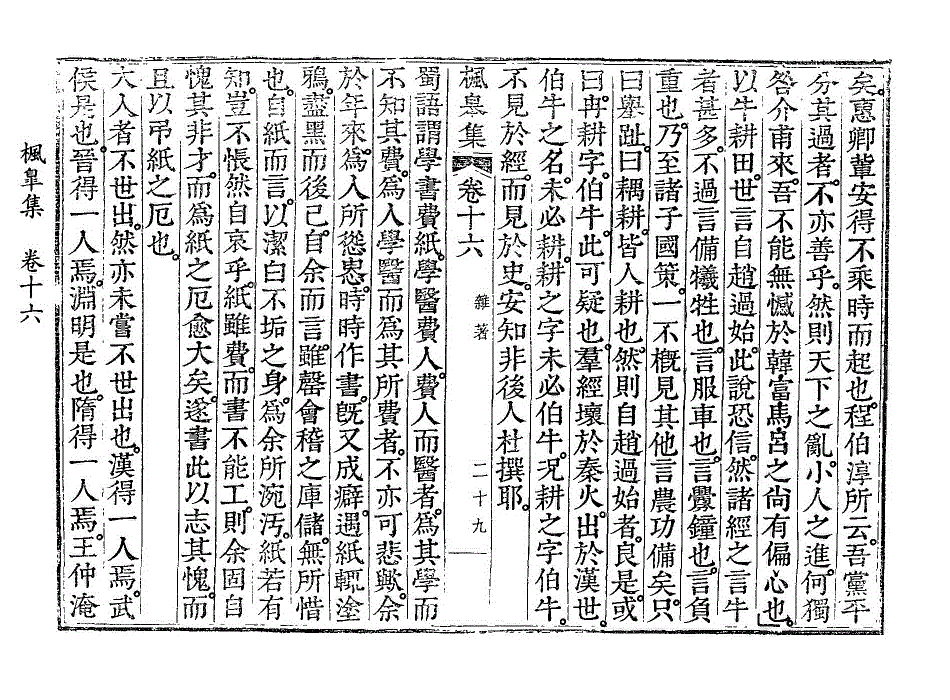 矣。惠卿辈安得不乘时而起也。程伯淳所云。吾党平分其过者。不亦善乎。然则天下之乱。小人之进。何独咎介甫来。吾不能无憾于韩,富,马,吕之尚有偏心也。以牛耕田。世言自赵过始。此说恐信。然诸经之言牛者甚多。不过言备牺牲也。言服车也。言衅钟也。言负重也。乃至诸子国策。一不概见其他言农功备矣。只曰举趾。曰耦耕。皆人耕也。然则自赵过始者。良是。或曰。冉耕字。伯牛。此可疑也。群经坏于秦火。出于汉世。伯牛之名。未必耕。耕之字未必伯牛。况耕之字伯牛。不见于经。而见于史。安知非后人杜撰耶。
矣。惠卿辈安得不乘时而起也。程伯淳所云。吾党平分其过者。不亦善乎。然则天下之乱。小人之进。何独咎介甫来。吾不能无憾于韩,富,马,吕之尚有偏心也。以牛耕田。世言自赵过始。此说恐信。然诸经之言牛者甚多。不过言备牺牲也。言服车也。言衅钟也。言负重也。乃至诸子国策。一不概见其他言农功备矣。只曰举趾。曰耦耕。皆人耕也。然则自赵过始者。良是。或曰。冉耕字。伯牛。此可疑也。群经坏于秦火。出于汉世。伯牛之名。未必耕。耕之字未必伯牛。况耕之字伯牛。不见于经。而见于史。安知非后人杜撰耶。蜀语谓学书费纸。学医费人。费人而医者。为其学而不知其费。为人学医而为其所费者。不亦可悲欤。余于年来。为人所怂恿。时时作书。既又成癖。遇纸辄涂鸦。尽黑而后已。自余而言。虽罄会稽之库储。无所惜也。自纸而言。以洁白不垢之身。为余所涴污。纸若有知。岂不怅然自哀乎。纸虽费。而书不能工。则余固自愧其非才。而为纸之厄愈大矣。遂书此以志其愧。而且以吊纸之厄也。
大人者不世出。然亦未尝不世出也。汉得一人焉。武侯是也。晋得一人焉。渊明是也。隋得一人焉。王仲淹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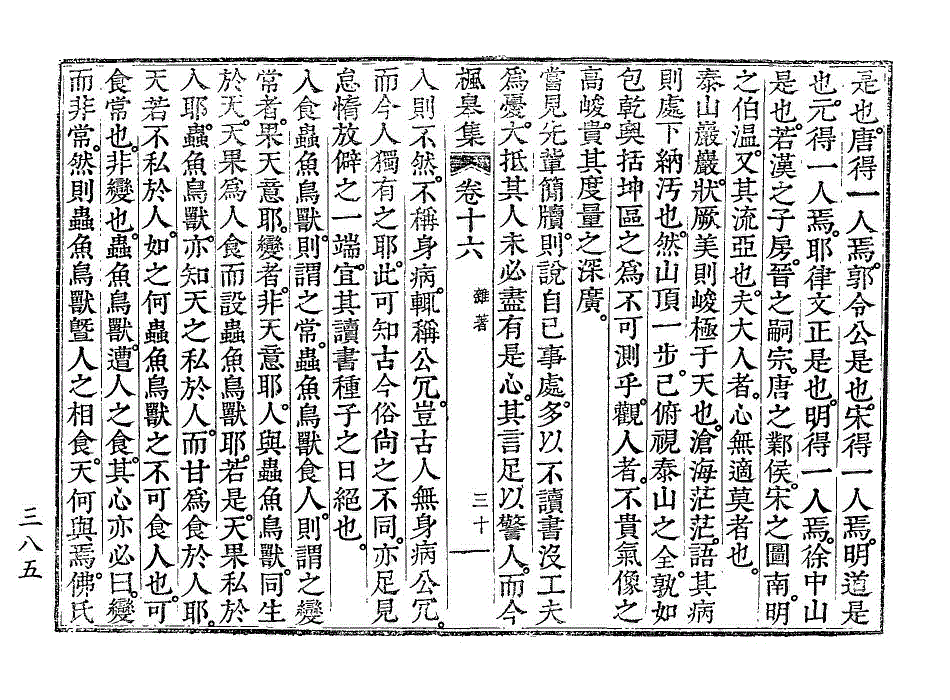 是也。唐得一人焉。郭令公是也。宋得一人焉。明道是也。元得一人焉。耶律文正是也。明得一人焉。徐中山是也。若汉之子房。晋之嗣宗。唐之邺侯。宋之图南。明之伯温。又其流亚也。夫大人者。心无适莫者也。
是也。唐得一人焉。郭令公是也。宋得一人焉。明道是也。元得一人焉。耶律文正是也。明得一人焉。徐中山是也。若汉之子房。晋之嗣宗。唐之邺侯。宋之图南。明之伯温。又其流亚也。夫大人者。心无适莫者也。泰山岩岩。状厥美则峻极于天也。沧海茫茫。语其病则处下纳污也。然山顶一步。已俯视泰山之全。孰如包乾奥括坤区之为不可测乎。观人者。不贵气像之高峻。贵其度量之深广。
尝见先辈简牍。则说自己事处。多以不读书没工夫为忧。大抵其人未必尽有是心。其言足以警人。而今人则不然。不称身病。辄称公冗。岂古人无身病公冗。而今人独有之耶。此可知古今俗尚之不同。亦足见怠惰放僻之一端。宜其读书种子之日绝也。
人食虫鱼鸟兽。则谓之常。虫鱼鸟兽食人。则谓之变常者。果天意耶。变者。非天意耶。人与虫鱼鸟兽。同生于天。天果为人食而设虫鱼鸟兽耶。若是。天果私于人耶。虫鱼鸟兽。亦知天之私于人。而甘为食于人耶。天若不私于人。如之何虫鱼鸟兽之不可食人也。可食常也。非变也。虫鱼鸟兽。遭人之食。其心亦必曰。变而非常。然则虫鱼鸟兽暨人之相食。天何与焉。佛氏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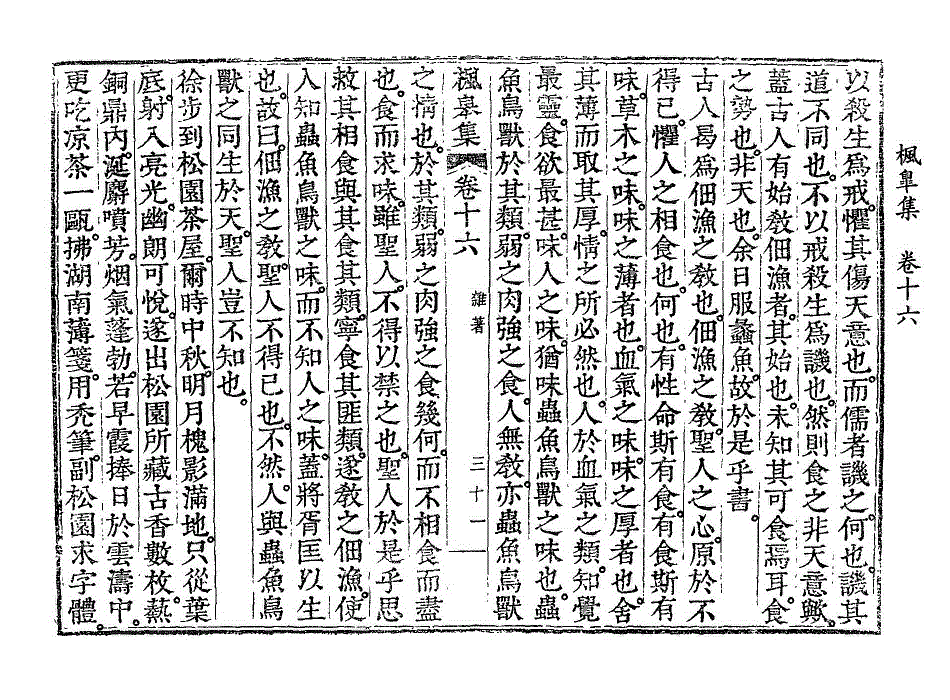 以杀生为戒。惧其伤天意也。而儒者讥之。何也。讥其道不同也。不以戒杀生为讥也。然则食之非天意欤。盖古人有始教佃渔者。其始也。未知其可食焉耳。食之势也。非天也。余日服蠡鱼。故于是乎书。
以杀生为戒。惧其伤天意也。而儒者讥之。何也。讥其道不同也。不以戒杀生为讥也。然则食之非天意欤。盖古人有始教佃渔者。其始也。未知其可食焉耳。食之势也。非天也。余日服蠡鱼。故于是乎书。古人曷为佃渔之教也。佃渔之教。圣人之心。原于不得已。惧人之相食也。何也。有性命斯有食。有食斯有味。草木之味。味之薄者也。血气之味。味之厚者也。舍其薄而取其厚。情之所必然也。人于血气之类。知觉最灵。食欲最甚。味人之味。犹味虫鱼鸟兽之味也。虫鱼鸟兽于其类。弱之肉强之食。人无教。亦虫鱼鸟兽之情也。于其类。弱之肉强之食几何。而不相食而尽也。食而求味。虽圣人。不得以禁之也。圣人于是乎思救其相食与其食其类。宁食其匪类。遂教之佃渔。使人知虫鱼鸟兽之味。而不知人之味。盖将胥匡以生也。故曰。佃渔之教。圣人不得已也。不然。人与虫鱼鸟兽之同生于天。圣人岂不知也。
徐步到松园茶屋。尔时中秋。明月槐影满地。只从叶底。射入亮光。幽朗可悦。遂出松园所藏古香数枚。爇铜鼎内。涎麝喷芳。烟气蓬勃。若早霞捧日于云涛中。更吃凉茶一瓯。拂湖南薄笺。用秃笔。副松园求字体。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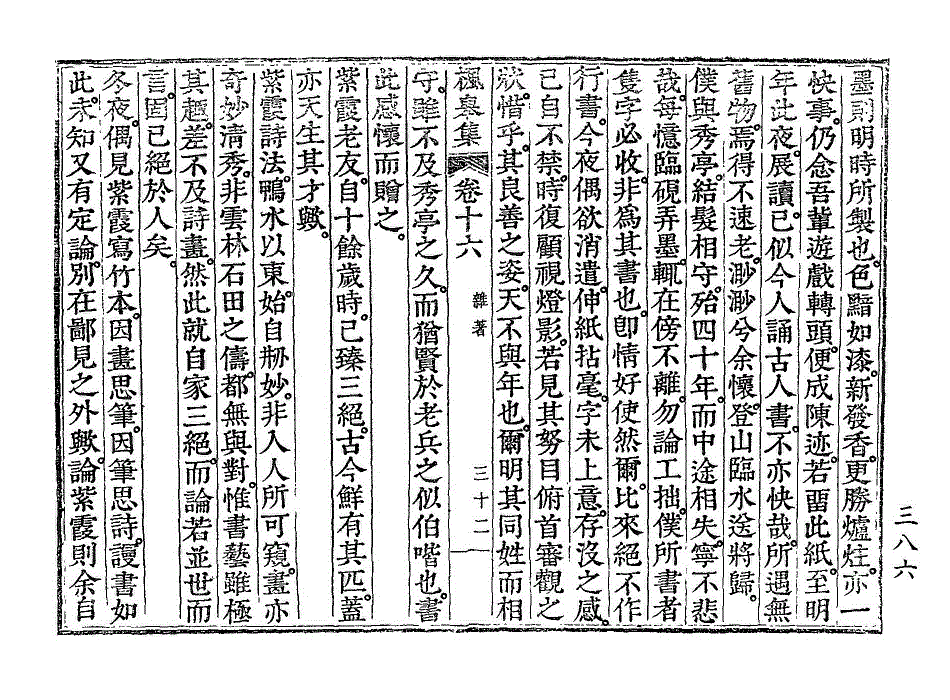 墨则明时所制也。色黯如漆。新发香。更胜炉炷。亦一快事。仍念吾辈游戏转头。便成陈迹。若留此纸。至明年此夜。展读。已似今人诵古人书。不亦快哉。所遇无旧物。焉得不速老。渺渺兮余怀。登山临水送将归。
墨则明时所制也。色黯如漆。新发香。更胜炉炷。亦一快事。仍念吾辈游戏转头。便成陈迹。若留此纸。至明年此夜。展读。已似今人诵古人书。不亦快哉。所遇无旧物。焉得不速老。渺渺兮余怀。登山临水送将归。仆与秀亭。结发相守。殆四十年。而中途相失。宁不悲哉。每忆临砚弄墨。辄在傍不离。勿论工拙。仆所书者只字必收。非为其书也。即情好使然尔。比来绝不作行书。今夜偶欲消遣。伸纸拈毫。字未上意。存没之感。已自不禁。时复顾视灯影。若见其努目俯首审观之状。惜乎。其良善之姿。天不与年也。尔明其同姓而相守。虽不及秀亭之久。而犹贤于老兵之似伯喈也。书此感怀而赠之。
紫霞老友。自十馀岁时。已臻三绝。古今鲜有其匹。盖亦天生其才欤。
紫霞诗法。鸭水以东。始自刱妙。非人人所可窥。画亦奇妙清秀。非云林石田之俦。都无与对。惟书艺虽极其趣。差不及诗画。然此就自家三绝。而论若并世而言。固已绝于人矣。
冬夜。偶见紫霞写竹本。因画思笔。因笔思诗。谩书如此。未知又有定论。别在鄙见之外欤。论紫霞则余自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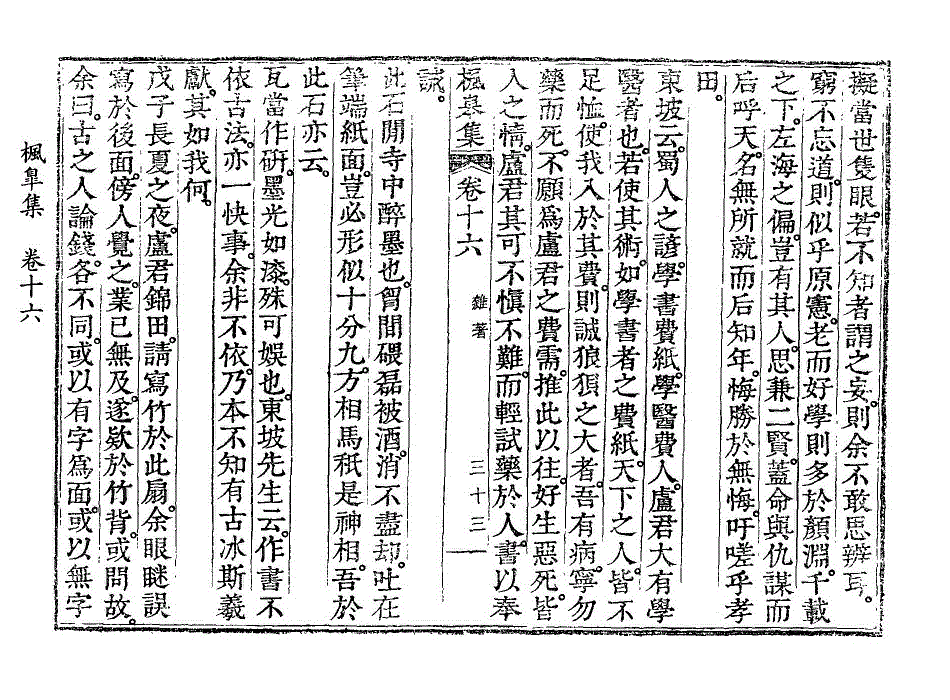 拟当世只眼。若不知者谓之妄。则余不敢思辨耳。
拟当世只眼。若不知者谓之妄。则余不敢思辨耳。穷不忘道。则似乎原宪。老而好学则多于颜渊。千载之下。左海之偏。岂有其人。思兼二贤。盖命与仇谋而后呼天。名无所就而后知年。悔胜于无悔。吁嗟乎孝田。
东坡云。蜀人之谚。学书费纸。学医费人。卢君大有学医者也。若使其术。如学书者之费纸。天下之人。皆不足恤。使我入于其费。则诚狼狈之大者。吾有病。宁勿药而死。不愿为卢君之费需。推此以往。好生恶死。皆人之情。卢君其可不慎不难。而轻试药于人。书以奉诫。
此石閒寺中醉墨也。胸间碨磊被酒。消不尽却。吐在笔端纸面。岂必形似十分九。方相马秖是神相。吾于此石亦云。
瓦当作研。墨光如漆。殊可娱也。东坡先生云。作书不依古法。亦一快事。余非不依。乃本不知有古冰斯羲献。其如我何。
戊子长夏之夜。卢君锦田。请写竹于此扇。余眼眯误写于后面。傍人觉之。业已无及。遂款于竹背。或问故。余曰。古之人论钱。各不同。或以有字为面。或以无字
枫皋集卷之十六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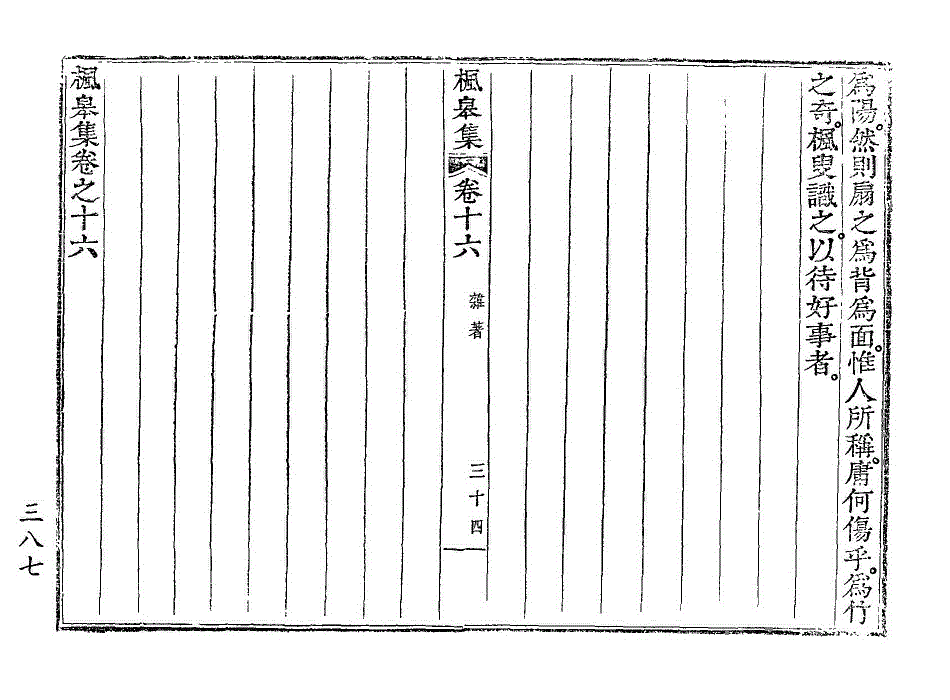 为阳。然则扇之为背为面。惟人所称。庸何伤乎。为竹之奇。枫叟识之。以待好事者。
为阳。然则扇之为背为面。惟人所称。庸何伤乎。为竹之奇。枫叟识之。以待好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