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浑斋集卷之四 第 x 页
浑斋集卷之四
书
书
浑斋集卷之四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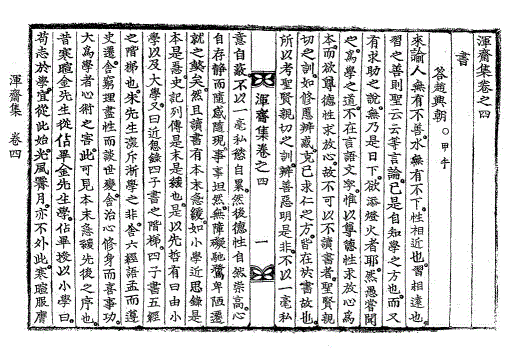 答赵兴朝(甲午)
答赵兴朝(甲午)来谕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之善则圣云云等言论。已是自知学之方也。而又有求助之说。无乃是日下。欲添灯火者耶。然愚尝闻之。为学之道。不在言语文字。惟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欲尊德性求放心。故不可以不读书者。圣贤亲切之训。如修慝辨惑。克己求仁之方。皆在于书故也。所以考圣贤亲切之训。辨善恶明是非。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然后德性自然崇高。心自存静而随感随现。事事坦然。无障碍驰骛卑陋迁就之弊矣。然且读书有本末急缓。如小学近思录是本是急。史记列传是末是缓也。是以先哲有曰由小学以及大学。又曰近思录四子书之阶梯。四子书五经之阶梯也。朱先生深斥浙学之非。舍六经语孟而遵史迁。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此可见本末急缓先后之序也。昔寒暄金先生从佔毕金先生学。佔毕授以小学曰。苟志于学。宜从此始。光风霁月。亦不外此。寒暄服膺
浑斋集卷之四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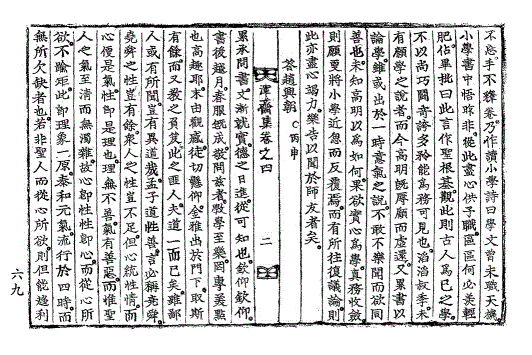 不忘。手不释卷。乃作读小学诗曰学文曾未职天机。小学书中悟昨非。从此尽心供子职。区区何必羡轻肥。佔毕批曰此言作圣根基。观此则古人为己之学。不以尚巧斗奇誇多矜能为务可见也。滔滔叔季。未有愿学之说者。而今高明既辱顾而虚还。又累书以论学。虽或出于一时意气之说。不敢不乐闻而欲同善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果欲实心为学。真务收敛。则愿更将小学近思而反覆焉。而有所往复议论。则此亦尽心竭力。乐告以闻于师友者矣。
不忘。手不释卷。乃作读小学诗曰学文曾未职天机。小学书中悟昨非。从此尽心供子职。区区何必羡轻肥。佔毕批曰此言作圣根基。观此则古人为己之学。不以尚巧斗奇誇多矜能为务可见也。滔滔叔季。未有愿学之说者。而今高明既辱顾而虚还。又累书以论学。虽或出于一时意气之说。不敢不乐闻而欲同善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果欲实心为学。真务收敛。则愿更将小学近思而反覆焉。而有所往复议论。则此亦尽心竭力。乐告以闻于师友者矣。答赵兴朝(丙申)
累承问书。文渐就实。德之日进。从可知也。钦仰钦仰。书后越月。春服既成。敬问玆者。敩学至乐。罔专美点也高趣耶。末由观感。徒切悬仰。金雅出于门下。取斯有馀。而又教之负笈。此之匪人。夫道一而已矣。虽鄙人或有所闻。岂有异道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尧舜之性岂有馀。众人之性岂不足。但心统性情。而心便是气。性即是理也。理无不善。气有善恶。而惟圣人之气至清而无浊杂。故心即性性即心。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此即理象一原。泰和元气。流行于四时。而无所欠缺者也。若非圣人而从心所欲。则但能趍利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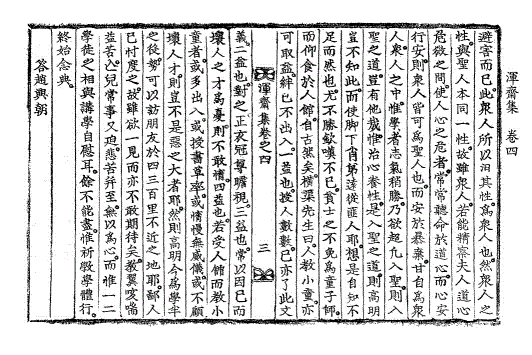 避害而已。此众人所以汩其性。为众人也。然众人之性。与圣人本同一性。故虽众人。若能精察夫人道心危微之间。使人心之危者。常常听命于道心。而心安行安。则众人皆可为圣人也。而安于暴弃。甘自为众人。众人之中。惟学者志气稍胜。乃欲超凡入圣。则入圣之道。岂有他哉。惟治心养性。是入圣之道。则高明岂不知此。而使脚下肖弟远从匪人耶。想是自知不足而然也。尤不胜钦叹不已。贫士之不免为童子师。而仰食于人馆。自古然矣。横渠先生曰。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数。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忧。则不敢惰。四益也。若受人馆而教小童者。或多出入。或授书草率。或惰慢无威仪。或不顾坏人才。则岂不是恶之大者耶。然则高明今为学半之役。势可以访朋友于四三百里不近之地耶。鄙人已忖度之。故虽欲一见而亦不敢期待矣。教翼咳喘益苦。亡儿常事又迫。悲苦并至。无以为心。而惟一二学徒之相与讲学自慰耳。馀不能尽。惟祈敩学体行。终始念典。
避害而已。此众人所以汩其性。为众人也。然众人之性。与圣人本同一性。故虽众人。若能精察夫人道心危微之间。使人心之危者。常常听命于道心。而心安行安。则众人皆可为圣人也。而安于暴弃。甘自为众人。众人之中。惟学者志气稍胜。乃欲超凡入圣。则入圣之道。岂有他哉。惟治心养性。是入圣之道。则高明岂不知此。而使脚下肖弟远从匪人耶。想是自知不足而然也。尤不胜钦叹不已。贫士之不免为童子师。而仰食于人馆。自古然矣。横渠先生曰。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数。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忧。则不敢惰。四益也。若受人馆而教小童者。或多出入。或授书草率。或惰慢无威仪。或不顾坏人才。则岂不是恶之大者耶。然则高明今为学半之役。势可以访朋友于四三百里不近之地耶。鄙人已忖度之。故虽欲一见而亦不敢期待矣。教翼咳喘益苦。亡儿常事又迫。悲苦并至。无以为心。而惟一二学徒之相与讲学自慰耳。馀不能尽。惟祈敩学体行。终始念典。答赵兴朝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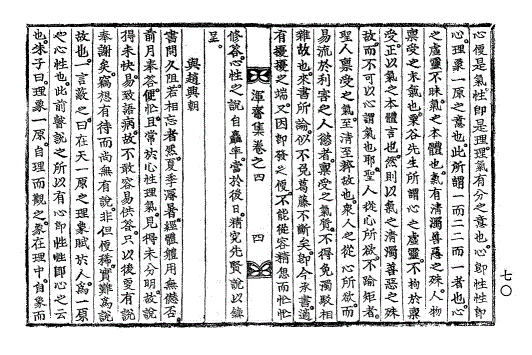 心便是气。性即是理。理气有分之意也。心即性性即心。理象一原之意也。此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心之虚灵不昧。气之本体也。气有清浊善恶之殊。人物禀受之末气也。栗谷先生所谓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受。正以气之本体言也。然则以气之清浊善恶之殊故。而不可以心谓气也耶。圣人从心所欲。不踰矩者。圣人禀受之气。至清至粹故也。众人之从心所欲。而易流于利害之人欲者。禀受之气质。不得免浊驳相杂故也。来书所论。似不免葛藤不断矣。即今承书。适有扰扰之端。又因即发之便。不能从容精思而忙忙修答。心性之说自粗率。当于后日。精究先贤说以录呈。
心便是气。性即是理。理气有分之意也。心即性性即心。理象一原之意也。此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心之虚灵不昧。气之本体也。气有清浊善恶之殊。人物禀受之末气也。栗谷先生所谓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受。正以气之本体言也。然则以气之清浊善恶之殊故。而不可以心谓气也耶。圣人从心所欲。不踰矩者。圣人禀受之气。至清至粹故也。众人之从心所欲。而易流于利害之人欲者。禀受之气质。不得免浊驳相杂故也。来书所论。似不免葛藤不断矣。即今承书。适有扰扰之端。又因即发之便。不能从容精思而忙忙修答。心性之说自粗率。当于后日。精究先贤说以录呈。与赵兴朝
书问久阻。若相忘者然。夏季溽暑。经体体用无𠎝否。前月奉答。便忙。且常于心性理气。见得未分明。故说得未快。易致语病。故不敢容易供答。只以后更有说奉谢矣。窃想有待而尚无有说。非但便稀。实难为说故也。一言蔽之。曰在天一原之理象赋于人。为一原之心性也。此前𥌒说之所以有心即性性即心之云也。朱子曰。理象一原。自理而观之。象在理中。自象而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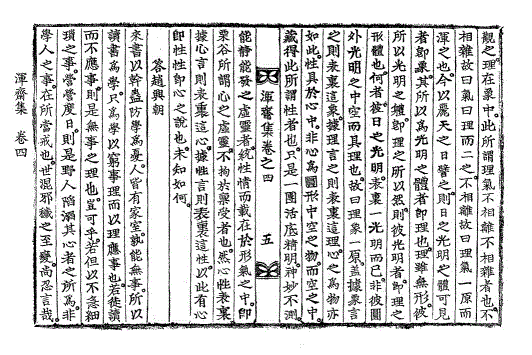 观之。理在象中。此所谓理气不相离不相杂者也。不相杂故曰气曰理而二之。不相离故曰理气一原而浑之也。今以丽天之日譬之。则日之光明之体可见者即象。其所以为光明之体者即理也。理虽无形。彼所以光明之体。即理之所以然。则彼光明者。即理之形体也。何者。彼日之光明。表里一光明而已。非彼圆外光明之中空而具理也。故曰理象一原。盖据象言之则表里这象。据理言之则表里这理。心之为物亦如此。性具于心中。非心为圆形中空之物。而空之中。藏得此所谓性者也。只是一团活底精明。神妙不测。能静能发之虚灵者。统性情而载在于形气之中。即栗谷所谓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受者也。然心性表里。据心言则表里这心。据性言则表里这性。以此有心即性性即心之说也。未知如何。
观之。理在象中。此所谓理气不相离不相杂者也。不相杂故曰气曰理而二之。不相离故曰理气一原而浑之也。今以丽天之日譬之。则日之光明之体可见者即象。其所以为光明之体者即理也。理虽无形。彼所以光明之体。即理之所以然。则彼光明者。即理之形体也。何者。彼日之光明。表里一光明而已。非彼圆外光明之中空而具理也。故曰理象一原。盖据象言之则表里这象。据理言之则表里这理。心之为物亦如此。性具于心中。非心为圆形中空之物。而空之中。藏得此所谓性者也。只是一团活底精明。神妙不测。能静能发之虚灵者。统性情而载在于形气之中。即栗谷所谓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受者也。然心性表里。据心言则表里这心。据性言则表里这性。以此有心即性性即心之说也。未知如何。答赵兴朝
来书以干蛊防学为忧。人皆有家室。孰能无事。所以读书为学。只为学以穷事理而以理应事也。若徒读而不应事。则是无事之理也。岂可乎。若但以不急细琐之事。营营度日。则是野人陷溺其心者之所为。非学人之事。在所当戒也。世混邪秽之至变。尚忍言哉。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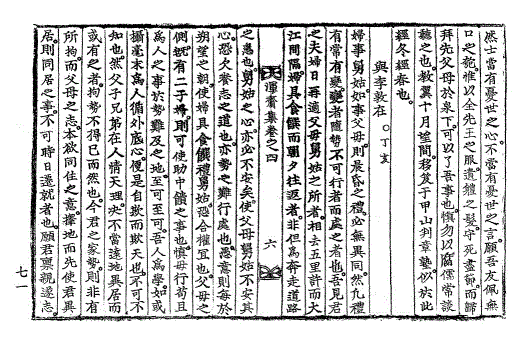 然士当有忧世之心。不当有忧世之言。愿吾友佩无口之匏。惟以全先王之服。遗体之发。守死尽节。而归拜先父母于泉下。可以了吾事也。慎勿以腐儒常谈听之也。教翼十月望间。移笈于甲山判章塾。似于此经冬经春也。
然士当有忧世之心。不当有忧世之言。愿吾友佩无口之匏。惟以全先王之服。遗体之发。守死尽节。而归拜先父母于泉下。可以了吾事也。慎勿以腐儒常谈听之也。教翼十月望间。移笈于甲山判章塾。似于此经冬经春也。与李敦在(丁亥)
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则晨昏之礼。必无异同。然凡礼有常有变。变者随势不可行者而处之者也。吾见君之夫妇日再适父母舅姑之所者。相去五里许而大江间隔。妇具食馔而朝夕往返者。非但为奔走道路之患也。舅姑之心。亦必不安矣。使父母舅姑不安其心。恐欠养志之道也。亦势之难行处也。愚意则每于朔望之朝。使妇具食馔礼舅姑。恐合权宜也。父母之侧。既有二子妇。则可使助中馈之事也。慎毋行苟且为人之事于势难及之地。至可至可。吾人为学。如或摄毫末为人循外底心。便是自欺而欺天也。不可不知也。然父子兄弟在人情天理。决不当远地异居而或有之者。拘势不得已而然也。今君之家势。则非有所拘。而父母之志。本欲同住之意。择地而先使君异居。则同居之事。不可时日迁就者也。愿君禀亲遂志。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2H 页
 以尽不可久之孝事也。读圣贤之书而汲汲行圣贤训辞者。今于君始见。故深有感于心。昨日面论。又此奉勖。古之人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则古人行步时。无不读书可知也。君于晨昏定省之行也。道里稍远。其往返之时。或不至闲游其心也耶。愚曾验之则夜或有思禀达之事。而未禀之前。诵读他书而铭念之。则或忘禀达之事而过时不及。或未即禀达而专念禀达之事。则又有妨于念书而温故没巴鼻者。亦非细事也。古之人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逮行之。又人臣之适公所也。书思对命于象笏。据此则吾辈亦当以粉板代笏。非但禀亲之事。虽他家间许多分付不可已之事。一一书之于板。或手执或置侧。时至而禀达者禀达。分付者分付。则必不至忘事。而亦不害看文念书矣。惟贤者留念。
以尽不可久之孝事也。读圣贤之书而汲汲行圣贤训辞者。今于君始见。故深有感于心。昨日面论。又此奉勖。古之人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则古人行步时。无不读书可知也。君于晨昏定省之行也。道里稍远。其往返之时。或不至闲游其心也耶。愚曾验之则夜或有思禀达之事。而未禀之前。诵读他书而铭念之。则或忘禀达之事而过时不及。或未即禀达而专念禀达之事。则又有妨于念书而温故没巴鼻者。亦非细事也。古之人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逮行之。又人臣之适公所也。书思对命于象笏。据此则吾辈亦当以粉板代笏。非但禀亲之事。虽他家间许多分付不可已之事。一一书之于板。或手执或置侧。时至而禀达者禀达。分付者分付。则必不至忘事。而亦不害看文念书矣。惟贤者留念。答李敦在(戊子)
敦在高祖宗孙无家无田。祖考宗孙亦无田。而惟敦在家亲勤劳得若干田地。视诸大小宗家。则富者也。今觉得义不可独富也。以如干田地。均分立产。无贫富不均之意。禀得亲命。但未知如何立规则可以为传家之美法乎。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2L 页
 所询之意。甚善甚善。子张子慕周彻法。而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云云。则纵不能验之一乡。然举行于一门。未为不可也。请仿张子之意。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先置祭田。(择最好田每位一日耕或半日耕。量田丰啬而为之似好。)次计人口实数。平均分田。(分田之际。或私意暂间。虽田亩均一。沃瘠不均。则非但主张者用心巧伪也。必将骨肉间生怨不赀。反致宗族不协之患矣。不可不知也。)后一宗人。合力通作。先治祭田。然后敢治私田。祭田所出则藏之别库。以供一岁之粢盛。且计私田所收每十亩。取其一亩之所出。藏之私库。以备不虞。则张子所谓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之事。自在其中。而亦符于彻法之遗意也。未知终能实践否。
所询之意。甚善甚善。子张子慕周彻法。而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云云。则纵不能验之一乡。然举行于一门。未为不可也。请仿张子之意。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先置祭田。(择最好田每位一日耕或半日耕。量田丰啬而为之似好。)次计人口实数。平均分田。(分田之际。或私意暂间。虽田亩均一。沃瘠不均。则非但主张者用心巧伪也。必将骨肉间生怨不赀。反致宗族不协之患矣。不可不知也。)后一宗人。合力通作。先治祭田。然后敢治私田。祭田所出则藏之别库。以供一岁之粢盛。且计私田所收每十亩。取其一亩之所出。藏之私库。以备不虞。则张子所谓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之事。自在其中。而亦符于彻法之遗意也。未知终能实践否。答李敦在(己丑)
近觉得虽学成君子。凡事一遵圣贤所示而行之。然后可以寡过。况以初学者好自立言。别设规模。岂不为妄作而反害心术耶。小学即日用笏记也。依而行之。而如欲行朝望之礼。则柳开中涂治家一节。甚平易简约。正好遵行。幸须去看也。然此事自读书好学之父兄倡振。然后庶可以不懈怠而有益。如或不然。而自其子弟强其不读书之父兄。如火急去做这个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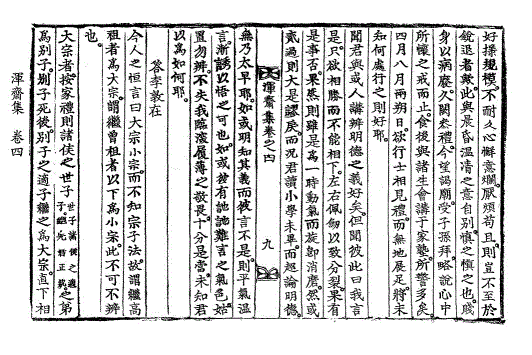 好㨾规模。不耐久心懈意烂。厌烦苟且。则岂不至于锐退者欤。此与晨昏温凊之意自别。慎之慎之也。贱身以病废。久阙参礼。今望谒庙。受子孙拜。略说心中所怀之戒而止。食后与诸生会讲于家塾。所警多矣。四月八月两朔日。欲行士相见礼。而无地展足。将未知何处行之则好耶。
好㨾规模。不耐久心懈意烂。厌烦苟且。则岂不至于锐退者欤。此与晨昏温凊之意自别。慎之慎之也。贱身以病废。久阙参礼。今望谒庙。受子孙拜。略说心中所怀之戒而止。食后与诸生会讲于家塾。所警多矣。四月八月两朔日。欲行士相见礼。而无地展足。将未知何处行之则好耶。闻君与或人讲辨明德之义好矣。但闻彼此曰我言是。只欲相胜而不能相下。左右佩剑以致分裂。果有是事否。果然则虽是为一时动气而旋即消磨。然或贰过则大是谬戾。而况君读小学未毕。而超论明德。无乃太早耶。如或明知其义而彼言不是。则平气温言。渐诱以悟之可也。如或彼有訑訑难言之气色。姑置勿辨。不失我临深履薄之敬畏。十分是当。未知君以为如何耶。
答李敦在
今人之恒言曰大宗小宗。而不知宗子法。故谓继高祖者为大宗。谓继曾祖者以下为小宗。此不可不辨也。
大宗者。按家礼则诸侯之世子(世子诸侯之适子。继先君正统。)之弟为别子。别子死后。别子之适子继之为大宗。直下相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3L 页
 传。百世不迁。此所谓大宗也。
传。百世不迁。此所谓大宗也。小宗者。别子之长子之弟死。则其死者之长子继之为小宗。小宗则五世而迁。是故有继祢之小宗。有继祖之小宗。有继曾祖之小宗。有继高祖之小宗。恐不可以大宗之名浑称于五世而迁之宗也。
又按小记陈注。别子有三。一是诸侯之适子之弟。别于正适。二是异姓公子来自他国。别于本国不来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为卿大夫而别于不仕者。皆称别子。(陈注止此。)然则非独诸侯之别子为大宗。凡继三别之宗。皆可谓之大宗。而且虽庶姓之家。有不祧之祖。则亦可谓之大宗也。
丧服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曷为后大宗也。尊之统也。
通典张湛曰礼所称为人后。后大宗。所以承正统。若非大宗所继。非正统之重。无相后之义。
通考徐乾学曰古礼大宗无子则立后。未有小宗无子而立后者也。小宗无后。古有从祖祔食之礼。则虽未尝继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绝也。
丧服传曰。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疏支子可也者。以其他家适子。固当自为小宗。故取支子。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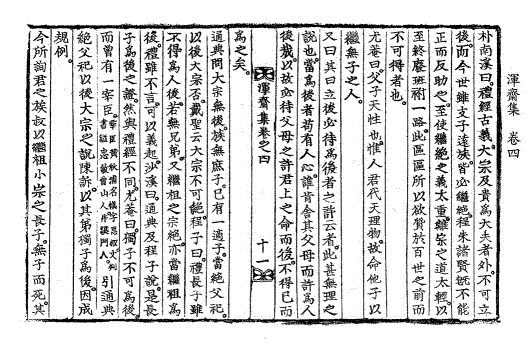 朴南溪曰。礼经古义。大宗及贵为大夫者外。不可立后。而今世虽支子远族。皆必继绝。程朱诸贤既不能正而反助之。至使继绝之义太重。离宗之道太轻。以至终废班祔一路。此区区所以欲质于百世之前而不可得者也。
朴南溪曰。礼经古义。大宗及贵为大夫者外。不可立后。而今世虽支子远族。皆必继绝。程朱诸贤既不能正而反助之。至使继绝之义太重。离宗之道太轻。以至终废班祔一路。此区区所以欲质于百世之前而不可得者也。尤庵曰。父子天性也。惟人君代天理物。故命他子以继无子之人。
又曰其曰立后必待为后者之许云者。此甚无理之说也。当为后者苟有人心。谁肯舍其父母而许为人后哉。以故必待父母之许君上之命而后。不得已而为之矣。
通典问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适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否。戴圣云大宗不可绝。程子曰。礼长子虽不得为人后。若无兄弟。又继祖之宗绝。亦当继祖为后。礼虽不言。可以义起。沙溪曰。通典及程子说。是长子为后之證。然与礼经不同。尤庵曰。独子不可为后。而曾有一宰臣。(宰臣黄秋浦名慎字思叔。文判书谥忠敏会山人。牛溪门人。)引通典绝父祀以后大宗之说陈诉。以其弟独子为后。因成规例。
今所询君之族叔以继祖小宗之长子。无子而死。其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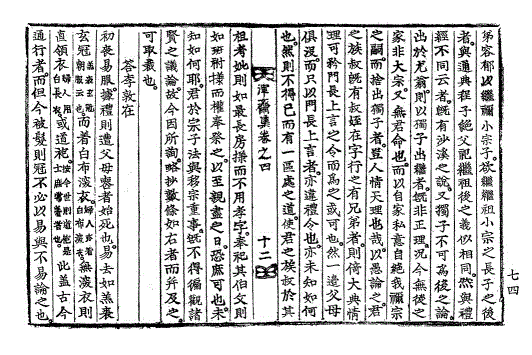 弟容郁以继祢小宗子。欲继继祖小宗之长子之后者。与通典程子绝父祀继祖后之义似相同。然与礼经不同云者。既有沙溪之说。又独子不可为后之论。出于尤翁。则以独子出继者。既非正理。况今无后之家非大宗。又无君命也。而以自家私意自绝我祢宗之嗣。而舍出独子者。岂人情天理也哉。以愚论之。君之族叔既有叔侄在字行之有兄弟者。则倚大典情理可矜门长上言之令而为之或可也。然一边父母俱没。而只以门长上言者。亦违礼令也。亦未知如何也。然则不得已而有一区处之道。使君之族叔于其祖考妣则如最长房㨾而不用孝字。奉祀其伯父则如班祔㨾而权奉祭之。以至亲尽之日。恐庶可也。未知如何耶。君于宗子法与移宗重事。既不得遍观诸贤之议论。故今因所询。略抄数条如右者而并及之。可取裁也。
弟容郁以继祢小宗子。欲继继祖小宗之长子之后者。与通典程子绝父祀继祖后之义似相同。然与礼经不同云者。既有沙溪之说。又独子不可为后之论。出于尤翁。则以独子出继者。既非正理。况今无后之家非大宗。又无君命也。而以自家私意自绝我祢宗之嗣。而舍出独子者。岂人情天理也哉。以愚论之。君之族叔既有叔侄在字行之有兄弟者。则倚大典情理可矜门长上言之令而为之或可也。然一边父母俱没。而只以门长上言者。亦违礼令也。亦未知如何也。然则不得已而有一区处之道。使君之族叔于其祖考妣则如最长房㨾而不用孝字。奉祀其伯父则如班祔㨾而权奉祭之。以至亲尽之日。恐庶可也。未知如何耶。君于宗子法与移宗重事。既不得遍观诸贤之议论。故今因所询。略抄数条如右者而并及之。可取裁也。答李敦在
初丧易服。据礼则遭父母丧者始死也。易去如羔裘玄冠(羔裘玄冠朝服云也。)而着白布深衣。(妇人亦着白布深衣。)无深衣则直领衣(妇人用白长衣。)或道袍。(按今世则道袍是士庶常着者也。)此盖古今通行者。而但今被发则冠不必以易与不易论之也。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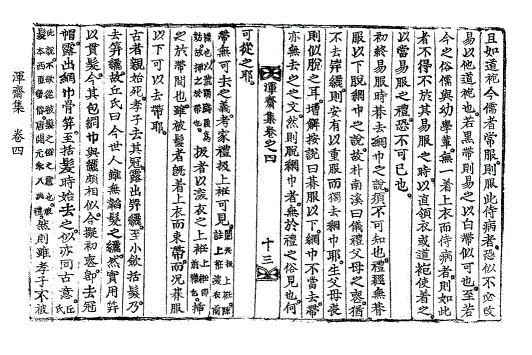 且如道袍今儒者常服。则服此侍病者。恐似不必改易以他道袍也。若黑带则易之以白带似可也。至若今之俗儒与幼学辈。无一着上衣而侍病者。则如此者不得不于其易服之时。以直领衣或道袍使着之。以当易服之礼。恐不可已也。
且如道袍今儒者常服。则服此侍病者。恐似不必改易以他道袍也。若黑带则易之以白带似可也。至若今之俗儒与幼学辈。无一着上衣而侍病者。则如此者不得不于其易服之时。以直领衣或道袍使着之。以当易服之礼。恐不可已也。初终易服时期去网巾之说。须不可知也。礼经无期服以下脱网巾之说。故朴南溪曰仪礼父母之丧。犹不去笄纚。则安有以重服而独去网巾耶。生父母丧则似脱之耳。增解按说曰期服以下。网巾不当去。带亦无去之之文。然则脱网巾者。无于礼之俗见也。何可从之耶。
带无可去之义。考家礼扱上衽可见。(问丧扱上衽。陈注上衽深衣前襟也。以号踊践履为妨。故插之于带也。)扱者以深衣之上衽(上衽即前襟也。)插之于带间也。虽被发者既着上衣而束带。而况期服以下可以去带耶。
古者亲始死。孝子去其冠。露出笄纚。至小敛括发。乃去笲纚。故丘氏曰今世人虽无韬发之纚。然实用笄以贯发。今其包网巾与纚颇相似。合拟初丧。即去冠帽。露出网巾骨笄。至括发时始去之。似亦同古意。(丘氏此说。不欲从被发之俗之意也。被发本西原蛮俗。唐开元采入兴礼。)然则虽孝子不被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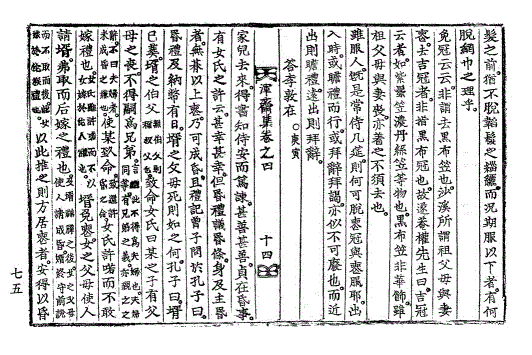 发之前。犹不脱韬发之缁纚。而况期服以下者。有何脱网巾之理乎。
发之前。犹不脱韬发之缁纚。而况期服以下者。有何脱网巾之理乎。免冠云云。非谓去黑布笠也。沙溪所谓祖父母与妻丧。去吉冠者。非指黑布冠也。故遂庵权先生曰。吉冠云者。如紫鬃笠浓丹丝笠等物也。黑布笠非华饰。虽祖父母与妻丧。亦着之不须去也。
虽服人。既是常侍几筵。则何可脱丧冠与丧服耶。出入时。或瞻礼而行。或拜辞拜谒。亦似不可废也。而近出则瞻礼。远出则拜辞。
答李敦在(庚寅)
家儿去来。得书知侍安而笃谏。甚善甚善。贞在昏事。有女氏之许云。甚幸甚幸。但昏礼议昏条。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丧。乃可成昏。且礼记曾子问于孔子曰。昏礼及纳币有日。婿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婿之伯父(无伯父则称叔父也。)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言▦(一作继)此不得为夫妇也。夫妇同等。有兄弟之义。亦亲之之辞。不曰夫妇者。未成昏之嫌也。 使某致命。(致还许昏之命。)女氏许喏而不敢嫁礼也。(女氏虽许喏而不以女嫁于佗人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及婿祥禫之后。女之父母使人请成昏。婿终守前说而不取而后。此女嫁于佗族礼也。)以此推之则方居丧者。安得以昏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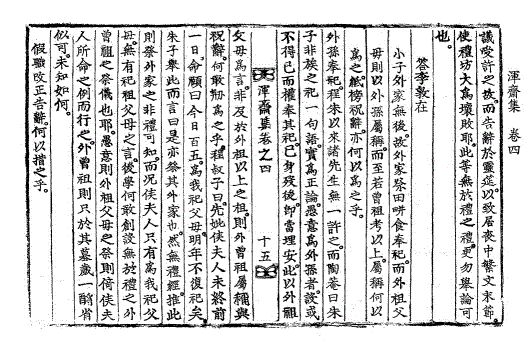 议受许之故。而告辞于灵筵。以致居丧中繁文末节。使礼坊大为坏败耶。此等无于礼之礼。更勿举论可也。
议受许之故。而告辞于灵筵。以致居丧中繁文末节。使礼坊大为坏败耶。此等无于礼之礼。更勿举论可也。答李敦在
小子外家无后。故外家祭田耕食奉祀。而外祖父母则以外孙属称。而至若曾祖考以上。属称何以为之。纸榜祝辞。亦何以为之乎。
外孙奉祀。程朱以来诸先生无一许之。而陶庵曰朱子非族之祀一句语。实为正论。愚意为外孙者。设或不得已而权奉其祀。己身殁后。即当埋安。此以外祖父母为言。非及于外祖以上之祖。则外曾祖属称与祝辞。何敢刱为之乎。程叔子曰。先妣侯夫人未终前一日。命颐曰今日百五。为我祀父母。明年不复祀矣。朱子举此而言曰是亦祭其外家也。然无礼经。推此则祭外家之非礼可知。而况侯夫人只有为我祀父母。无有祀祖父母之言。后学何敢创设无于礼之外曾祖之祭仪也耶。愚意则外祖父母之祭则倚侯夫人所命之例而行之。外曾祖则只于其墓岁一酹省似可。未知如何。
假职改正告辞。何以措之乎。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6L 页
 假职改正告辞。当曰维岁次云云。显某亲府君。府君在世。既无受职。至于殁后。又无赠职。妄称俗例之假职。欺天罔上。孰甚于此。今始觉非。不胜惶恐。今因朔参。改题学生。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
假职改正告辞。当曰维岁次云云。显某亲府君。府君在世。既无受职。至于殁后。又无赠职。妄称俗例之假职。欺天罔上。孰甚于此。今始觉非。不胜惶恐。今因朔参。改题学生。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与李源在(丁亥)
昨者令从学淳质以渠之出继事。渠则不欲出继而亲命迫切。此将奈何。愚乃出示圣贤训辞及 本朝令甲。则学淳也喜得启发其良心之说而大悟曰。家亲从俗例而私相与受。而一边父母年岁今过七旬矣。自有家亲之许。自知有子。而一门人亦皆曰某为某之子云。在小子之道。既闻大义则何可独自心知其然。而不明告其不可为后之本心。使一门内。将致纷纷之是非于一边父母不讳之后耶。愿先生为小子。代作其不可为后之文字于一边如何。愚乃思之。义理似甚完转也。乃代草以给。因教学淳转示贤者者。贤者与渠为族。而知能助明大义之昧没者而左右之故也。闻贤者一览文字。而曰义理虽如此。时俗皆私相与受云。而多有不满之说。岂意贤者而有如此低仰之说。使左右之视听者。眩乱邪正而不分别耶。大抵天下之大事。孰如绝人父子之恩。移以继他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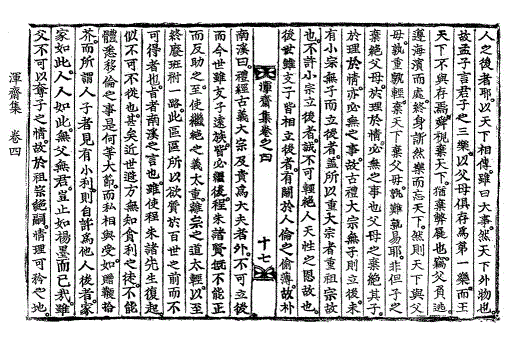 人之后者耶。以天下相传。虽曰大事。然天下外物也。故孟子言君子之三乐。以父母俱存为第一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舜视弃天下。犹弃弊屣也。窃父负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下与父母。孰重孰轻。弃天下弃父母。孰难孰易耶。非但子之弃绝父母。于理于情。必无之事也父母之弃绝其子。于理于情。亦必无之事。故古礼大宗无子则立后。未有小宗无子而立后者。盖所以重大宗者重祖宗故也。不许小宗立后者。诚不可轻绝人天性之恩故也。后世虽支子皆相立后者。有关于人伦之偷薄。故朴南溪曰。礼经古义大宗及贵为大夫者外。不可立后。而今世虽支子远族。皆必继后。程朱诸贤既不能正而反助之。至使继绝之义太重。离宗之道太轻。以至终废班祔一路。此区区所以欲质于百世之前而不可得者也。旨者南溪之言也。虽使程朱诸先生复起。似不可不从也。甚矣近世遐方无知贪利之徒。不能体悉移伦之事是何等大节。而私相与受。如赠鞭拾芥。而所谓人子者见有小利。则自许为他人后者。家家如此。人人如此。无父无君。岂止如杨墨而已哉。虽父不可以夺子之情。故于祖宗绝嗣。情理可矜之地。
人之后者耶。以天下相传。虽曰大事。然天下外物也。故孟子言君子之三乐。以父母俱存为第一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舜视弃天下。犹弃弊屣也。窃父负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下与父母。孰重孰轻。弃天下弃父母。孰难孰易耶。非但子之弃绝父母。于理于情。必无之事也父母之弃绝其子。于理于情。亦必无之事。故古礼大宗无子则立后。未有小宗无子而立后者。盖所以重大宗者重祖宗故也。不许小宗立后者。诚不可轻绝人天性之恩故也。后世虽支子皆相立后者。有关于人伦之偷薄。故朴南溪曰。礼经古义大宗及贵为大夫者外。不可立后。而今世虽支子远族。皆必继后。程朱诸贤既不能正而反助之。至使继绝之义太重。离宗之道太轻。以至终废班祔一路。此区区所以欲质于百世之前而不可得者也。旨者南溪之言也。虽使程朱诸先生复起。似不可不从也。甚矣近世遐方无知贪利之徒。不能体悉移伦之事是何等大节。而私相与受。如赠鞭拾芥。而所谓人子者见有小利。则自许为他人后者。家家如此。人人如此。无父无君。岂止如杨墨而已哉。虽父不可以夺子之情。故于祖宗绝嗣。情理可矜之地。浑斋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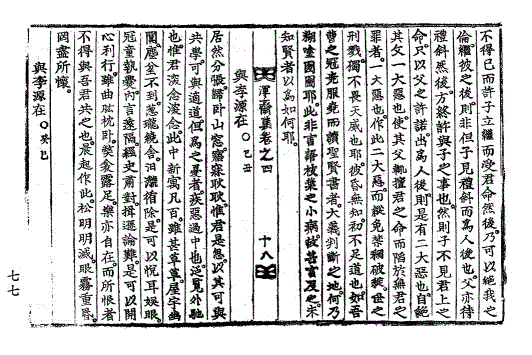 不得已而许子立继而受君命然后。乃可以绝我之伦。继彼之后。则非但子见礼斜而为人后也。父亦待礼斜然后。方终许与子之事也。然则子不见君上之命。只以父之许诺。出为人后。则是有二大恶也。自绝其父一大恶也。使其父辄擅君之命而陷于无君之罪者。一大恶也。作此二大恶。而纵免禁网破绽。世之形戮。独不畏天威也耶。彼昏无知。初不足道也。如吾曹之冠尧服尧而读圣贤书者。大义判断之地。何乃糊涂囫囵耶。此非言语枝叶之小病。故甚言及之。未知贤者以为如何耶。
不得已而许子立继而受君命然后。乃可以绝我之伦。继彼之后。则非但子见礼斜而为人后也。父亦待礼斜然后。方终许与子之事也。然则子不见君上之命。只以父之许诺。出为人后。则是有二大恶也。自绝其父一大恶也。使其父辄擅君之命而陷于无君之罪者。一大恶也。作此二大恶。而纵免禁网破绽。世之形戮。独不畏天威也耶。彼昏无知。初不足道也。如吾曹之冠尧服尧而读圣贤书者。大义判断之地。何乃糊涂囫囵耶。此非言语枝叶之小病。故甚言及之。未知贤者以为如何耶。与李源在(己丑)
居然分张。归卧山窗。寤寐耿耿。惟君是思。以其可与共学。可与适道。但为之忧者。疾恶过中也。泛览外驰也。惟君深念深念。此中新寓凡百。虽甚草草。屋宇幽阒。尘坌不到。葱珑绕舍。汩㶁循除。是可以悦耳娱眼。冠童执爨。内言远隔。经史肃对。揖逊论难。是可以开心利行。虽曲肱枕卧。弊衾露足。乐亦自在。而所恨者不得与吾君共之也。晨起作此。松明明灭。眼雾重昏。罔尽所怀。
与李源在(癸巳)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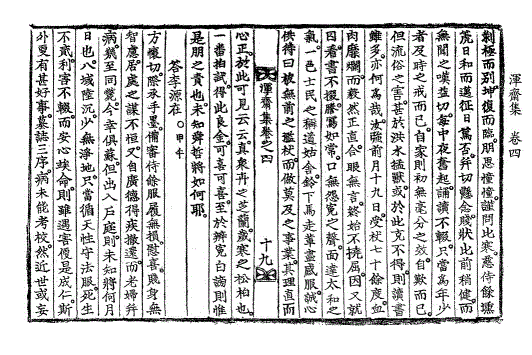 剥极而别。坤复而临。朋思憧憧。谨问比寒。慈侍馀埙篪日和而迈征日笃否。并切悬念。贱状比前稍健。而无闻之叹益切。每中夜奋起。诵读不辍。只当为年少者及时之戒而已。自家则初无毫分之效。自叹而已。但流俗之害。甚于洪水猛兽。或于此克不得。则读书虽多。亦何为哉。汝强前月十九日。受杖七十馀度。血肉糜烂。而毅然正直。合眼无言。终始不挠屈。因又就囚。看书不掇。誊写如常。口无怨冤之声。面达太和之气。一邑士民之称道姑舍。铃下马走辈尽感服。诚心供待曰被无前之滥杖。而做莫及之事业。其理直而心正。于此可见云云。真众卉之芝兰。岁寒之松柏也。一番拍试。得此良金。可喜可喜。至于辨冤白谤则惟是朋之责也。未知舜哲将如何耶。
剥极而别。坤复而临。朋思憧憧。谨问比寒。慈侍馀埙篪日和而迈征日笃否。并切悬念。贱状比前稍健。而无闻之叹益切。每中夜奋起。诵读不辍。只当为年少者及时之戒而已。自家则初无毫分之效。自叹而已。但流俗之害。甚于洪水猛兽。或于此克不得。则读书虽多。亦何为哉。汝强前月十九日。受杖七十馀度。血肉糜烂。而毅然正直。合眼无言。终始不挠屈。因又就囚。看书不掇。誊写如常。口无怨冤之声。面达太和之气。一邑士民之称道姑舍。铃下马走辈尽感服。诚心供待曰被无前之滥杖。而做莫及之事业。其理直而心正。于此可见云云。真众卉之芝兰。岁寒之松柏也。一番拍试。得此良金。可喜可喜。至于辨冤白谤则惟是朋之责也。未知舜哲将如何耶。答李源在(甲午)
方怀切。际承手墨。备审侍馀服履无损。慰喜。贱身无智虑。居处之谋不恒。又自广德得疾撤还。而老妇并病。几至同毙。今幸俱苏。但出入户庭。则未知将何月日也。八域陆沉。少无净地。只当循天性守法服。死生不贰。利害不辍。而安心俟命。则虽遇害便是成仁。斯外更有甚好事。墓志三序。病未能考校。然近世或妄
浑斋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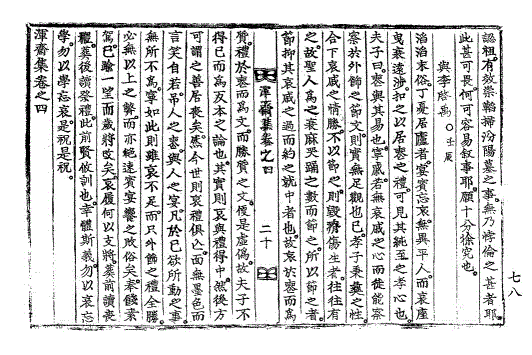 认祖。有效崇韬扫汾阳墓之事。无乃悖伦之甚者耶。此甚可畏。何可容易叙事耶。愿十分徐究也。
认祖。有效崇韬扫汾阳墓之事。无乃悖伦之甚者耶。此甚可畏。何可容易叙事耶。愿十分徐究也。与李启禹(壬辰)
滔滔末俗。丁忧居庐者。宴宾忘哀。无异平人。而哀座曳衰远涉。扣之以居丧之礼。可见其纯至之孝心也。夫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若无哀戚之心而徒能察察于外饰之节文。则实无足观也已。孝子秉彝之性。合下哀戚之情胜。不以节之。则毁瘠伤生者。往往有之。故圣人为之衰麻哭踊之数而节之。所以节之者。节抑其哀戚之过而约之就中者也。故哀于丧而为质。礼于丧而为文。而胜质之文。便是虚伪。故夫子不得已而为反本之论也。其实则哀与礼得中。然后方可谓之善居丧矣。然今世则哀礼俱亡。面无墨色而言笑自若。吊人之丧。与人之宴。凡于己欲所动之事。无所不为。宁如此则虽哀不足。而只外饰之礼全胜。必无以上之弊。而亦绝速宾宴飨之败俗矣。奉饯素驾。已踰一望而岁将改矣。哀履何以支将。葬前读丧礼。葬后读祭礼。此前贤攸训也。幸体斯义。勿以哀忘学。勿以学忘哀。是祝是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