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浑斋集卷之七 第 x 页
浑斋集卷之七
书
书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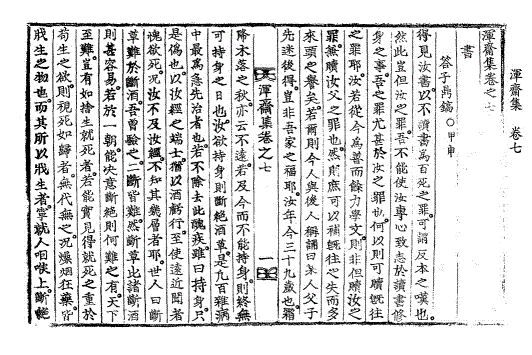 答子鼎镐(甲申)
答子鼎镐(甲申)得见汝书。以不读书为百死之罪。可谓反本之叹也。然此岂但汝之罪。吾不能使汝专心致志于读书修身之事。吾之罪尤甚于汝之罪也。何以则可赎既往之罪耶。汝若从今为善而馀力学文。则非但赎汝之罪。兼赎汝父之罪也。然则庶可以补既往之失而多来头之誉矣。若尔则今人与后人称诵曰某人父子先迷后得。岂非吾家之福耶。汝年今三十九岁也。霜降木落之秋。亦云不远。若及今而不能持身。则终无可持身之日也。汝欲持身则断绝酒草。是凡百杂病中最为急先治者也。若不除去此丑疾。虽曰持身。只是伪也。以汝经之端士。犹以酒亏行。至使远近闻者愧欲死。况汝不及汝经。不知其几层者耶。世人曰断草难于断酒。吾曾验之。二断皆难。然断草比诸断酒则甚容易。若于一朝。能决意断绝则何难之有。天下至难。岂有如舍生就死者。若能实见得就死之重于苟生之欲。则视死如归者。无代无之。况燥烟狂药。皆戕生之物也。而其所以戕生者。宁就人咽喉上。断绝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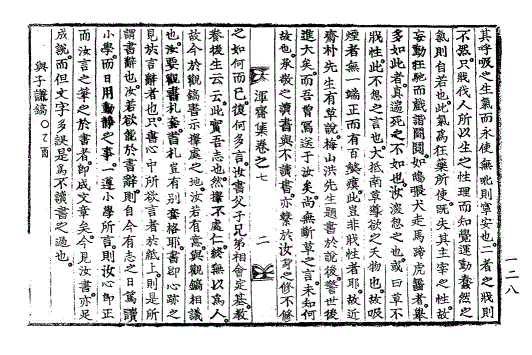 其呼吸之生气而永使无吪则宁安也。二者之戕则不然。只戕伐人所以生之性理而知觉运动蠢然之气则自若也。此气为狂药所使。既失其主宰之性。故妄动狂驰而戏谐斗阋。如䲭张犬走马蹄虎齧者。举多如此者。真遄死之不如也。汝深思之也。或曰草不戕性。此不思之言也。大抵南草导欲之夭物也。故吸烟者无一端正而有百㢢瘼。此岂非戕性者耶。故近斋朴先生有草说。梅山洪先生题书于说后。警世后进大矣。而吾曾写送于汝矣。尚无断草之言。未知何故也。承敬之读书与不读书。亦系于汝身之修不修之如何而已。复何多言。汝书父子兄弟相会定基。教养后生云云。此实吾志也。然择不处仁。终无以为人。故今于观镐书示择处之地。汝若有意。与观镐相议也。汝要观书札套。书札岂有别套格耶。书即心迹之见于言辞者也。只书心中所欲言者于纸上。则是所谓书辞也。汝若欲能于书辞。则自今有志之日笃读小学。而日用动静之事。一遵小学所言。则汝心即正而汝言之笔之于书者。即成文章矣。今见汝书。亦足成说。而但文字多误。是为不读书之过也。
其呼吸之生气而永使无吪则宁安也。二者之戕则不然。只戕伐人所以生之性理而知觉运动蠢然之气则自若也。此气为狂药所使。既失其主宰之性。故妄动狂驰而戏谐斗阋。如䲭张犬走马蹄虎齧者。举多如此者。真遄死之不如也。汝深思之也。或曰草不戕性。此不思之言也。大抵南草导欲之夭物也。故吸烟者无一端正而有百㢢瘼。此岂非戕性者耶。故近斋朴先生有草说。梅山洪先生题书于说后。警世后进大矣。而吾曾写送于汝矣。尚无断草之言。未知何故也。承敬之读书与不读书。亦系于汝身之修不修之如何而已。复何多言。汝书父子兄弟相会定基。教养后生云云。此实吾志也。然择不处仁。终无以为人。故今于观镐书示择处之地。汝若有意。与观镐相议也。汝要观书札套。书札岂有别套格耶。书即心迹之见于言辞者也。只书心中所欲言者于纸上。则是所谓书辞也。汝若欲能于书辞。则自今有志之日笃读小学。而日用动静之事。一遵小学所言。则汝心即正而汝言之笔之于书者。即成文章矣。今见汝书。亦足成说。而但文字多误。是为不读书之过也。与子谦镐(乙酉)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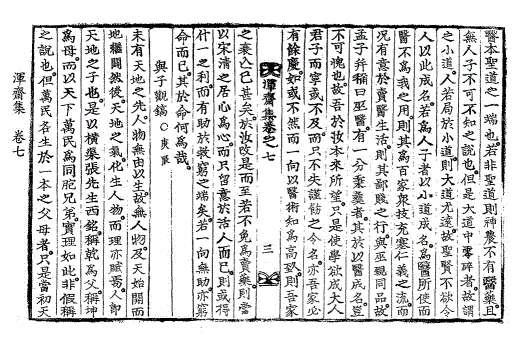 医本圣道之一端也。若非圣道则神农不有医药。且无人子不可不知之说也。但是大道中零碎者。故谓之小道。人若局于小道。则大道尤远。故圣贤不欲令人以此成名。若为人子者以小道成名。为医所使而医不为我之用。则其为百家众技充塞仁义之流。而况有意于卖医生活。则其鄙贱之行。与巫觋同品。故孟子并称曰巫医。有一分秉彝者。其于以医成名。岂不可愧也。故吾于汝本来所望。只是使学欲成大人君子而宁或不及。而只不失谨饬之令名。亦吾家必有馀庆。如或不然而一向以医术知为高致。则吾家之衰亡已甚矣。于汝改是而至若不免为卖药。则当以宋清之居心为心。而只留意于活人而已。则或得什一之利。而有助于救穷之端矣。若一向无助。亦穷命而已。其于命何为哉。
医本圣道之一端也。若非圣道则神农不有医药。且无人子不可不知之说也。但是大道中零碎者。故谓之小道。人若局于小道。则大道尤远。故圣贤不欲令人以此成名。若为人子者以小道成名。为医所使而医不为我之用。则其为百家众技充塞仁义之流。而况有意于卖医生活。则其鄙贱之行。与巫觋同品。故孟子并称曰巫医。有一分秉彝者。其于以医成名。岂不可愧也。故吾于汝本来所望。只是使学欲成大人君子而宁或不及。而只不失谨饬之令名。亦吾家必有馀庆。如或不然而一向以医术知为高致。则吾家之衰亡已甚矣。于汝改是而至若不免为卖药。则当以宋清之居心为心。而只留意于活人而已。则或得什一之利。而有助于救穷之端矣。若一向无助。亦穷命而已。其于命何为哉。与子观镐(庚辰)
未有天地之先。人物无由以生。故无人物。及天始开而地继辟然后。天地之气。化生人物。而理亦赋焉。人即天地之子也。是以横渠张先生西铭。称乾为父。称坤为母。而以天下万民为同胞兄弟。实理如此。非假称之说也。但万民各生于一本之父母者。只是当初天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29L 页
 地之气。化生男女之后。男女之形。相交媾精而各生男女。即所谓形化而生者也。是故虽千万夫妇而亿兆民生。实皆父乾母坤同胞以生者也。天下之民。若是乎皆我同胞。故虽行路底人。见其饥者寒者。则自然生恻隐之心。见其鳏独失所者。则自然动哀矜不忍之情。因以有拯济衣被之念发焉。是岂勉强苦思以得来者哉。人之秉彝良心。本来自然如此也。是以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于行路人犹如是。而况于同父祖兄弟从族。何忍以粗底气习相加而伤恩害义也耶。且况今此乱离苍黄之世界。骨肉兄弟之閒。少相乖戾而少相失和。则尤何以相扶颠也耶。惟汝鼎镐与谦镐与观镐泰镐同心勉励。同与汝从兄。互相难疑。互相出谋。患难贫穷。一心拯济。得少美味。必相会食。期以同死生同苦乐为心。虽我死之后。终身勿衰。则先父母之苗裔。安得不昌大乎。惟汝辈恻念恻念也。
地之气。化生男女之后。男女之形。相交媾精而各生男女。即所谓形化而生者也。是故虽千万夫妇而亿兆民生。实皆父乾母坤同胞以生者也。天下之民。若是乎皆我同胞。故虽行路底人。见其饥者寒者。则自然生恻隐之心。见其鳏独失所者。则自然动哀矜不忍之情。因以有拯济衣被之念发焉。是岂勉强苦思以得来者哉。人之秉彝良心。本来自然如此也。是以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于行路人犹如是。而况于同父祖兄弟从族。何忍以粗底气习相加而伤恩害义也耶。且况今此乱离苍黄之世界。骨肉兄弟之閒。少相乖戾而少相失和。则尤何以相扶颠也耶。惟汝鼎镐与谦镐与观镐泰镐同心勉励。同与汝从兄。互相难疑。互相出谋。患难贫穷。一心拯济。得少美味。必相会食。期以同死生同苦乐为心。虽我死之后。终身勿衰。则先父母之苗裔。安得不昌大乎。惟汝辈恻念恻念也。与子观镐(丁亥)
未知汝于近日。更如何立规程耶。朱子答潘叔昌书曰。尝窃私怪。彼中朋友。不肯于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实下工夫。而泛观博取于一时议论之閒。所以头绪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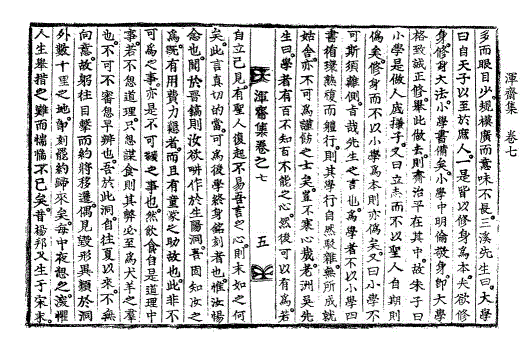 多而眼目少。规模广而意味不长。三溪先生曰。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夫欲修身。修身大法。小学书备矣。小学中明伦敬身。即大学格致诚正修。举此做去。则齐治平在其中。故朱子曰小学是做人底㨾子。又曰立志而不以圣人自期则伪矣。修身而不以小学为本则亦伪矣。又曰小学不可斯须离侧。旨哉先生之言也。为学者不以小学四书循环熟复而体行。则其学行自然驳杂。无所成就姑舍。亦不可为谨饬之士矣。岂不寒心哉。老洲吴先生曰。学者有百不知百不能之心。然后可以有为。若自立己见。有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之心。则末如之何矣。此言真切的当。可为后学终身铭刻者也。惟汝惕念也。闻于晋镐则汝欲耕作于生阳洞。吾固知汝之为。既有用费力恳者。而且有童蒙之助故也。此非不可为之事。亦是不可缓之事也。然饮食自是道理中事。若不思道理。只思谋食则其弊必至为犬羊之群也。不可不审思早辨也。吾于此洞。自往夏以来。不无向意。故躬往目击而约将移迁。偶见毁形异类于洞外数十里之地。即刻罢约归来矣。每中夜思之。深惧人生举措之难而惴惴不已矣。昔杨邦乂生于宋末。
多而眼目少。规模广而意味不长。三溪先生曰。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夫欲修身。修身大法。小学书备矣。小学中明伦敬身。即大学格致诚正修。举此做去。则齐治平在其中。故朱子曰小学是做人底㨾子。又曰立志而不以圣人自期则伪矣。修身而不以小学为本则亦伪矣。又曰小学不可斯须离侧。旨哉先生之言也。为学者不以小学四书循环熟复而体行。则其学行自然驳杂。无所成就姑舍。亦不可为谨饬之士矣。岂不寒心哉。老洲吴先生曰。学者有百不知百不能之心。然后可以有为。若自立己见。有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之心。则末如之何矣。此言真切的当。可为后学终身铭刻者也。惟汝惕念也。闻于晋镐则汝欲耕作于生阳洞。吾固知汝之为。既有用费力恳者。而且有童蒙之助故也。此非不可为之事。亦是不可缓之事也。然饮食自是道理中事。若不思道理。只思谋食则其弊必至为犬羊之群也。不可不审思早辨也。吾于此洞。自往夏以来。不无向意。故躬往目击而约将移迁。偶见毁形异类于洞外数十里之地。即刻罢约归来矣。每中夜思之。深惧人生举措之难而惴惴不已矣。昔杨邦乂生于宋末。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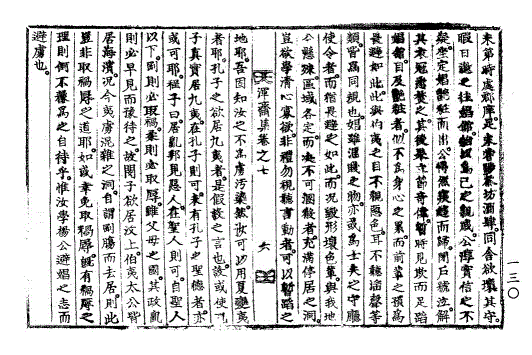 未第时处郡庠。足未尝步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暇日邀之往娼馆。始以为己之亲戚。公淳实信之不疑。坐定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趍而归。闭户号泣。解其衣冠悉焚之。其后果立节奇伟。暂时见欺而足蹈娼馆。目及艳妆者。似不为身心之累。而前辈之预为畏避如此。此与伯夷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等类。皆为同规也。娼虽淫贱之物。亦或为士夫之守厅使令者。而犹畏避之如此。而况毁形坏色辈。与我地分悬殊。区域各定。而决不可溷殽者。充满停居之洞。岂欲学清心寡欲。非礼勿视听言动者。可以暂蹈之地耶。吾固知汝之不为虏污染。然汝可以用夏变夷者耶。孔子之欲居九夷者。是假设之言也。设或使孔子真实居九夷。在孔子则可。未有孔子之圣德者。亦或可耶。程子曰。居乱邦见恶人。在圣人则可。自圣人以下。刚则必取祸。柔则必取辱。虽父母之国。其政乱则必早见而豫待之。故闵子欲居汶上。伯夷太公皆居海滨。况今夷虏混杂之洞。自谓刚肠而去居。则此岂非取祸辱之道耶。如或幸免取祸辱。既有祸辱之理则何不豫为之自待乎。惟汝学杨公避娼之志而避虏也。
未第时处郡庠。足未尝步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暇日邀之往娼馆。始以为己之亲戚。公淳实信之不疑。坐定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趍而归。闭户号泣。解其衣冠悉焚之。其后果立节奇伟。暂时见欺而足蹈娼馆。目及艳妆者。似不为身心之累。而前辈之预为畏避如此。此与伯夷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等类。皆为同规也。娼虽淫贱之物。亦或为士夫之守厅使令者。而犹畏避之如此。而况毁形坏色辈。与我地分悬殊。区域各定。而决不可溷殽者。充满停居之洞。岂欲学清心寡欲。非礼勿视听言动者。可以暂蹈之地耶。吾固知汝之不为虏污染。然汝可以用夏变夷者耶。孔子之欲居九夷者。是假设之言也。设或使孔子真实居九夷。在孔子则可。未有孔子之圣德者。亦或可耶。程子曰。居乱邦见恶人。在圣人则可。自圣人以下。刚则必取祸。柔则必取辱。虽父母之国。其政乱则必早见而豫待之。故闵子欲居汶上。伯夷太公皆居海滨。况今夷虏混杂之洞。自谓刚肠而去居。则此岂非取祸辱之道耶。如或幸免取祸辱。既有祸辱之理则何不豫为之自待乎。惟汝学杨公避娼之志而避虏也。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1H 页
 与子观镐
与子观镐地理之说有两非。谓无地理而不为祖考遗体。以广求吉兆而务为体魄之安宁者非也。谓有地理而全以祖考遗体。为子孙富贵之资而力求吉兆者非也。二者之心。固皆忘亲而薄于亲者。初不当论其优劣。然自其亡者遗骨之安苦言之。则为求富贵者之祖考者或幸也。何者。冢中致凶不一。或为地风所翻。头骨异处散亡。或翻棺覆尸而吹沙没尸。或木根眯其目。缠缚其全体。或为火气所薰。骨色如黑炭者有焉。或为冷气所冻者有焉。或水满冢中。或蚁满棺中。或毛生全骨者有焉。或尸化为蛇豕者有焉。而此非但风水者之说然也。余之目击而證验者颇多。而如右炭色半焚之尸骨。更求吉兆藏之而后几年启验。则骨色还白。一凶一吉。皆地气致然。而有气有理。则谓无地理而不为祖考之藏而求吉者。岂非孟浪者耶。仁人孝子闻他人祖考之遗体。值逢凶祸之变。而其恻怛爱哀之情。岂不反思其祖考之藏而动出来遏不得欤。以恻怛爱哀之情。为祖考之藏而求吉之际。岂有为傍人求福之讥说而避嫌。不欲广求术士博访名山耶。但仁人孝子为先求山之道。与惑于祸福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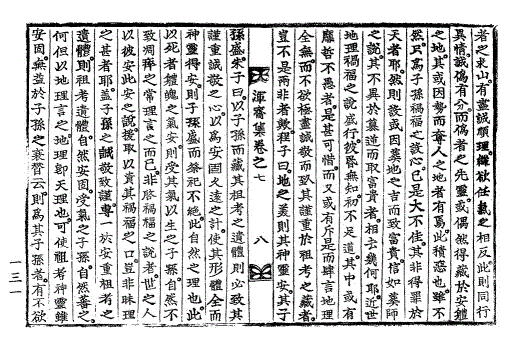 者之求山。有尽诚顺理。纵欲任气之相反。此则同行异情。诚伪有分。而伪者之先灵。或偶然得藏于安体之地。其或因势而夺人之地者有焉。此积恶也。虽不然。只为子孙祸福之设心。已是大不佳。其非得罪于天者耶。然则设或因葬地之吉而致富贵。信如葬师之说。其不异于篡逆而取富贵者。相去几何耶。近世地理祸福之说盛行。彼昏无知。初不足道。其中或有靡哲不愚者。是甚可惜。而又或有斥是而肆言地理全无。而不欲极尽诚敬而致其谨重于祖考之藏者。岂不是两非者欤。程子曰。地之美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朱子曰。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此以死者体魄之气安。则受其气以生之子孙。自然不致凋瘁之常理言之而已。非启祸福之说者。世之人以彼安此安之说。援取以资其祸福之口。岂非昧理之甚者耶。盖子孙之诚敬致谨。专一于安重祖考之遗体。则祖考遗体。自然安固。受气之子孙。自然蕃之。何但以地理言之。地理即天理也。可使祖考神灵虽安固。无益于子孙之衰替云。则为其子孙者。有不欲
者之求山。有尽诚顺理。纵欲任气之相反。此则同行异情。诚伪有分。而伪者之先灵。或偶然得藏于安体之地。其或因势而夺人之地者有焉。此积恶也。虽不然。只为子孙祸福之设心。已是大不佳。其非得罪于天者耶。然则设或因葬地之吉而致富贵。信如葬师之说。其不异于篡逆而取富贵者。相去几何耶。近世地理祸福之说盛行。彼昏无知。初不足道。其中或有靡哲不愚者。是甚可惜。而又或有斥是而肆言地理全无。而不欲极尽诚敬而致其谨重于祖考之藏者。岂不是两非者欤。程子曰。地之美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朱子曰。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此以死者体魄之气安。则受其气以生之子孙。自然不致凋瘁之常理言之而已。非启祸福之说者。世之人以彼安此安之说。援取以资其祸福之口。岂非昧理之甚者耶。盖子孙之诚敬致谨。专一于安重祖考之遗体。则祖考遗体。自然安固。受气之子孙。自然蕃之。何但以地理言之。地理即天理也。可使祖考神灵虽安固。无益于子孙之衰替云。则为其子孙者。有不欲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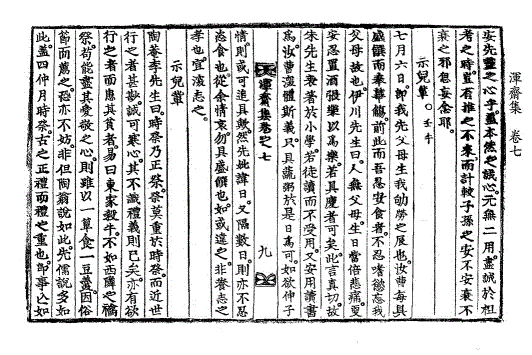 安先灵之心乎。盖本然之诚心。元无二用。尽诚于祖考之时。岂有推之不来。而计较子孙之安不安衰不衰之邪思妄念耶。
安先灵之心乎。盖本然之诚心。元无二用。尽诚于祖考之时。岂有推之不来。而计较子孙之安不安衰不衰之邪思妄念耶。示儿辈(壬午)
七月六日。即我先父母生我劬劳之辰也。汝曹每具盛馔而奉华觞。前此而吾忍安食者。不忍嗜欲忘我父母故也。伊川先生曰。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矣。此言真切。故朱先生表著于小学。若徒读而不受用。又安用读书为。汝曹深体斯义。只具蔬粥于是日为可。如欲伸子情。则或可追具欤。然先妣讳日。又隔数日。则亦不忍恣食也。从余情哀。勿具盛馔也。如或违之。非养志之孝也。宜深志之。
示儿辈
陶庵李先生曰。时祭乃正祭。祭莫重于时祭。而近世行之者甚鲜。诚可寒心。其不识礼义则已矣。亦有欲行之者而患其贫者。易曰东家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苟能尽其爱敬之心。则虽以一箪食一豆羹。因俗节而荐之。恐亦不妨。非但陶翁说如此。先儒说多如此。盖四仲月时祭。古之正礼而礼之重也。即事亡如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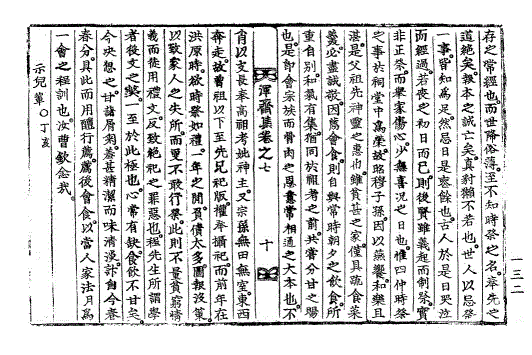 存之常经也。而世降俗薄。至不知时祭之名。奉先之道绝矣。报本之诚亡矣。真豺獭不若也。世人以忌祭一事。皆知为足。然忌日是丧馀也。古人于是日哭泣而经过。若丧之初日而已。则后贤虽义起而制祭。实非正祭。而举家伤心。少无喜况之日也。惟四仲时祭之事于祠堂中为荣。故昭穆子孙。因以燕飨。和乐且湛。是父祖先神灵之惠也。虽贫甚之家。仅具疏食菜羹。必尽诚敬。因荐会食。则自与常时朝夕之饮食。所重自别。和气有集。犹同于祖考之前。共尝分甘之赐也。是即会宗族而骨肉之恩意常相通之大本也。不肖以支长奉高祖考妣神主。又宗孙无田无室。东西奔走。故曾祖以下至先兄祀版。权奉摄祀。而前年在洪原时。欲时祭如礼。一年之閒。负债太多。图报没策。以致家人之失所。而更不敢行祭。此则不量贫穷情义而徒用礼文。反致绝祀之罪恶也。程先生所谓学者役文之弊。一至于此极也。心常有缺。食饮不甘矣。今决思之。甘藷屑匊。羞甚精洁而味清淡。计自今春春分。具此而用醴行荐。荐后会食。以当人家法月为一会之程训也。汝曹钦念哉。
存之常经也。而世降俗薄。至不知时祭之名。奉先之道绝矣。报本之诚亡矣。真豺獭不若也。世人以忌祭一事。皆知为足。然忌日是丧馀也。古人于是日哭泣而经过。若丧之初日而已。则后贤虽义起而制祭。实非正祭。而举家伤心。少无喜况之日也。惟四仲时祭之事于祠堂中为荣。故昭穆子孙。因以燕飨。和乐且湛。是父祖先神灵之惠也。虽贫甚之家。仅具疏食菜羹。必尽诚敬。因荐会食。则自与常时朝夕之饮食。所重自别。和气有集。犹同于祖考之前。共尝分甘之赐也。是即会宗族而骨肉之恩意常相通之大本也。不肖以支长奉高祖考妣神主。又宗孙无田无室。东西奔走。故曾祖以下至先兄祀版。权奉摄祀。而前年在洪原时。欲时祭如礼。一年之閒。负债太多。图报没策。以致家人之失所。而更不敢行祭。此则不量贫穷情义而徒用礼文。反致绝祀之罪恶也。程先生所谓学者役文之弊。一至于此极也。心常有缺。食饮不甘矣。今决思之。甘藷屑匊。羞甚精洁而味清淡。计自今春春分。具此而用醴行荐。荐后会食。以当人家法月为一会之程训也。汝曹钦念哉。示儿辈(丁亥)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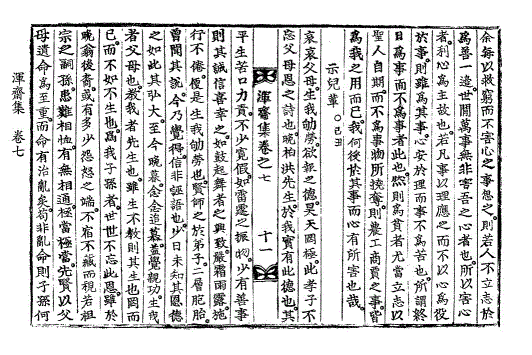 余每以救穷而不害心之事思之。则若人不立志于为善一边。世閒万事无非害吾之心者也。所以害心者。利心为主故也。若凡事以理应之而不以心为役于事。则虽为其事。心安于理而事不为苦也。所谓终日为事而不为事者此也。然则为贫者尤当立志以圣人自期。而不为事物所挠夺。则农工商贾之事。皆为我之用而已。我何役于其事而心有所害也哉。
余每以救穷而不害心之事思之。则若人不立志于为善一边。世閒万事无非害吾之心者也。所以害心者。利心为主故也。若凡事以理应之而不以心为役于事。则虽为其事。心安于理而事不为苦也。所谓终日为事而不为事者此也。然则为贫者尤当立志以圣人自期。而不为事物所挠夺。则农工商贾之事。皆为我之用而已。我何役于其事而心有所害也哉。示儿辈(己丑)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此孝子不忘父母恩之诗也。晚柏洪先生。于我实有此德也。其平生苦口力责。不少宽假。如雷霆之振物。少有善事则其诚信喜幸之。如鼓起舞者之兴致。严霜雨露。施行不倦。便是生我劬劳也。贤师之于弟子。二层胞胎。曾闻其说。今乃觉得。信非诬语也。少日未知其恩德之如此其弘大。至今晚暮。念念追慕。益觉亲切。生我者父母也。教我者先生也。虽生不教则其生也罔而已。而不如不生也。为我子孙者。世世不忘此恩。虽于晚翁后裔。或有多少怨怒之端。不宿不藏而视若祖宗之嗣孙。患难相恤。有无相通。极当极当。先贤以父母遗命为至重。而命有治乱矣。苟非乱命则子孙何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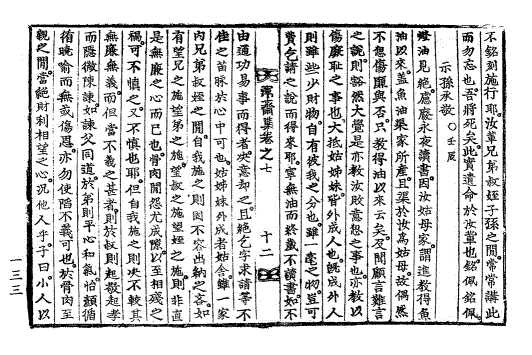 不铭刻施行耶。汝辈兄弟叔侄子孙之閒。常常讲此而勿忘也。吾将死矣。此实遗命于汝辈也。铭佩铭佩。
不铭刻施行耶。汝辈兄弟叔侄子孙之閒。常常讲此而勿忘也。吾将死矣。此实遗命于汝辈也。铭佩铭佩。示孙承敬(壬辰)
灯油见绝。虑废永夜读书。因汝姑母家。谓进教得鱼油以来。盖鱼油渠家所产。且渠于汝为姑母。故偶然不思伤廉与否。只教得油以来云矣。及闻顾言难言之说。则豁然大觉是亦教汝败意思之事也。亦教以伤廉耻之事也。大抵姑姊妹。皆外成人也。既成外人则虽些少财物。自有彼我之分也。虽一毫之物。岂可费乞请之说而得来耶。宁无油而终岁不读书。如不由通功易事而得者。决意却之。且绝乞字求请等不佳之苗脉于心中可也。姑姊妹外成者姑舍。虽一家内兄弟叔侄之閒。自我施之则固不容出纳之吝。如有望兄之施望弟之施。望叔之施望侄之施。则非直是无廉之心而已也。骨肉閒怨尤成隙。以至相残之祸。可不慎之。又不慎也耶。但自我施之则决不较其无廉无义。而但当不义之甚者。则于叔则起敬起孝而隐微陈谏。如谏父同道。于弟则平心和气。怡颜循循晓喻而无或伤恩。亦勿使陷不义可也。于骨肉至亲之閒。当绝财利相望之心。况他人乎。子曰。小人以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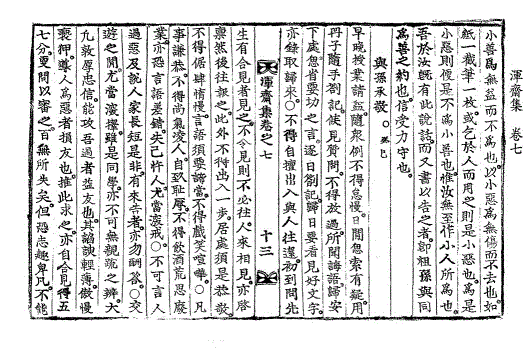 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也。如纸一截笔一枚。或乞于人而用之则是小恶也。为是小恶则便是不为小善也。惟汝无至作小人所为也。吾于汝既有此说话。而又书以告之者。即祖孙与同为善之约也。信受力守也。
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也。如纸一截笔一枚。或乞于人而用之则是小恶也。为是小恶则便是不为小善也。惟汝无至作小人所为也。吾于汝既有此说话。而又书以告之者。即祖孙与同为善之约也。信受力守也。与孙承敬(癸巳)
早晚授业请益。随众例不得怠慢。日閒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劄记。候见质问。不得放过。所闻诲语。归安下处。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记。归日要看见好文字。亦录取归来。○不得自擅出入与人往还。初到问先生有合见者见之。不令见则不必往。人来相见。亦启禀然后往报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处须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语须要谛当。不得戏笑喧哗。○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致耻辱。不得饮酒荒思废业。亦恐言语差错。失己忤人。尤当深戒。○不可言人过恶及说人家长短是非。有来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閒。尤当深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见得五七分。更问以审之。百无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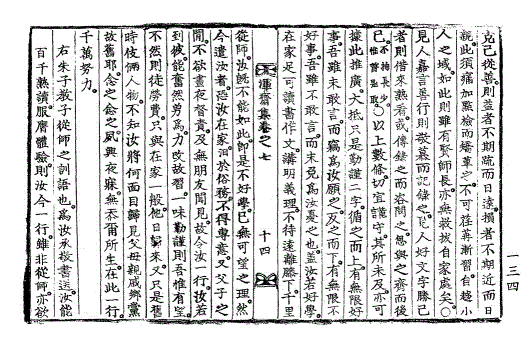 克己从善。则益者不期疏而日远。损者不期近而日亲。此须痛加点检而矫革之。不可荏苒渐习。自趍小人之域。如此则虽有贤师长。亦无救拔自家处矣。○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不拘长少。惟善是取。)○以上数条。切宜谨守。其所未及。亦可据此推广。大抵只是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虽未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虽不敢言。而未免为汝忧之也。盖汝若好学。在家足可读书作文。讲明义理。不待远离膝下。千里从师。汝既不能如此。即是不好学。已无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于俗务。不得专意。又父子之閒。不欲昼夜督责。及无朋友闻见。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奋然勇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惟有望。不然则徒劳费。只与在家一般。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不知汝将何面目归见父母亲戚乡党故旧耶。念之念之。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在此一行。千万努力。
克己从善。则益者不期疏而日远。损者不期近而日亲。此须痛加点检而矫革之。不可荏苒渐习。自趍小人之域。如此则虽有贤师长。亦无救拔自家处矣。○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不拘长少。惟善是取。)○以上数条。切宜谨守。其所未及。亦可据此推广。大抵只是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虽未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虽不敢言。而未免为汝忧之也。盖汝若好学。在家足可读书作文。讲明义理。不待远离膝下。千里从师。汝既不能如此。即是不好学。已无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于俗务。不得专意。又父子之閒。不欲昼夜督责。及无朋友闻见。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奋然勇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惟有望。不然则徒劳费。只与在家一般。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不知汝将何面目归见父母亲戚乡党故旧耶。念之念之。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在此一行。千万努力。右朱子教子从师之训语也。为汝承敬书送。汝能百千熟读。服膺体验。则汝今一行。虽非从师。亦欲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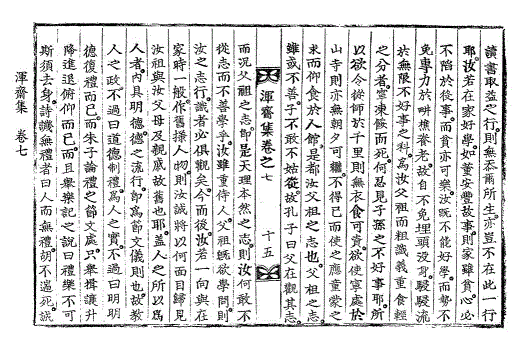 读书取益之行。则无忝尔所生。亦岂不在此一行耶。汝若在家好学。如董安丰故事。则家虽贫。心必不陷于役事。而贫亦可乐。汝既不能好学。而势不免专力于耕樵养老。故自不免埋头没身。骎骎流于无限不好事之科。为汝父祖而粗识义重食轻之分者。宁冻馁而死。何忍见子孙之不好事耶。所以欲令从师于千里则无衣食可资。欲使宁处于山寺则亦无朝夕可继。不得已而使之应童蒙之求而仰食于人馆。是都汝父祖之志也。父祖之志。虽或不善。子不敢不姑从。故孔子曰父在观其志。而况父祖之志。即是天理本然之志。则汝何敢不从志而不善学乎。汝虽重侍人。父祖既欲学问。则汝之志行。识者必俱观矣。今而后。汝若一向与在家时一般。作旧㨾人物。则汝诚将以何面目归见汝祖与汝父母及亲戚故旧也耶。盖人之所以为人者。内具明德。德之流行。即为节文仪则也。故教人之政。不过曰道德制礼。为人之实。不过曰明明德复礼而已。而朱子论礼之节文处。只举揖让升降进退俯仰而已。而且举乐记之说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诗讥无礼者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诚
读书取益之行。则无忝尔所生。亦岂不在此一行耶。汝若在家好学。如董安丰故事。则家虽贫。心必不陷于役事。而贫亦可乐。汝既不能好学。而势不免专力于耕樵养老。故自不免埋头没身。骎骎流于无限不好事之科。为汝父祖而粗识义重食轻之分者。宁冻馁而死。何忍见子孙之不好事耶。所以欲令从师于千里则无衣食可资。欲使宁处于山寺则亦无朝夕可继。不得已而使之应童蒙之求而仰食于人馆。是都汝父祖之志也。父祖之志。虽或不善。子不敢不姑从。故孔子曰父在观其志。而况父祖之志。即是天理本然之志。则汝何敢不从志而不善学乎。汝虽重侍人。父祖既欲学问。则汝之志行。识者必俱观矣。今而后。汝若一向与在家时一般。作旧㨾人物。则汝诚将以何面目归见汝祖与汝父母及亲戚故旧也耶。盖人之所以为人者。内具明德。德之流行。即为节文仪则也。故教人之政。不过曰道德制礼。为人之实。不过曰明明德复礼而已。而朱子论礼之节文处。只举揖让升降进退俯仰而已。而且举乐记之说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诗讥无礼者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诚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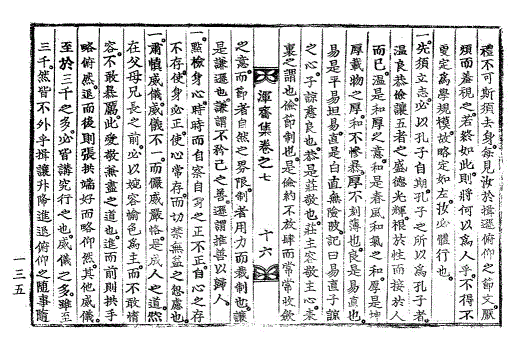 礼不可斯须去身。每见汝于揖逊俯仰之节文。厌烦而羞视之。若终如此。则将何以为人乎。不得不更定为学规模。故略定如左。汝必体行也。
礼不可斯须去身。每见汝于揖逊俯仰之节文。厌烦而羞视之。若终如此。则将何以为人乎。不得不更定为学规模。故略定如左。汝必体行也。一。先须立志。必以孔子自期。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者。温良恭俭让五者之盛德光辉。根于性而接于人而已。温是和厚之意。和是春风和气之和。厚是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厚不刻薄也。良是易直也。易是平易坦易。直是白直无险陂。记曰易直子谅之心。子谅慈良也。恭是庄敬也。庄主容敬主心。表里之谓也。俭节制也。是俭约不放肆而常常收敛之意。而节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也。让是谦逊也。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善以归人。
一。点检身心。时时而自察自身之正不正。自心之存不存。使身必正。使心常存。而切禁无益之思虑也。
一。肃慎成仪。威仪不一。而俨威严恪。是成人之道。然在父母兄长之前。必以婉容愉色为主。而不敢惰容。不敢暴厉。此爱敬兼尽之道也。进而前则拱手略俯然。退而后则张拱端好而略仰然。其他威仪。至于三千之多。必皆讲究行之也。威仪之多。虽至三千。然皆不外乎揖让升降进退俯仰之随事随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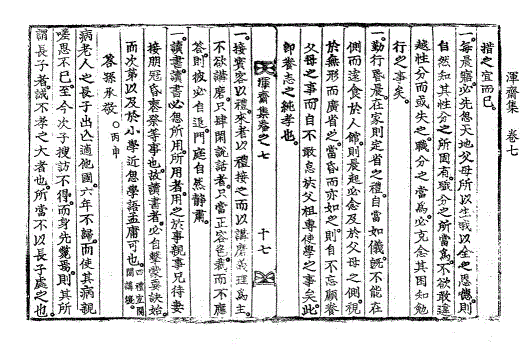 措之宜而已。
措之宜而已。一。每晨寤。必先思天地父母所以生我以全之恩德。则自然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不欲敢违越性分而或失之。职分之当为。必克念其困知勉行之事矣。
一。勤行昏晨。在家则定省之礼。自当如仪。既不能在侧而远食于人馆。则晨起必念及于父母之侧。视于无形而广省之。当昏而亦如之。则自不忘顾养父母之事。而自不敢怠于父祖专使学之事矣。此即养志之纯孝也。
一。接宾客以礼。来者以礼接之而以讲磨义理为主。不欲讲磨。只肆闲说话者。只当正容色。裁而不应答。则彼必自退。门庭自然静肃。
一。读书。读书必思所用。所用者。用之于事亲事兄待妻接朋冠昏丧祭等事也。故读书者。必自击蒙要诀始。而次第以及于小学近思学语孟庸可也。(四礼宜閒閒讲复。)
答孙承敬(丙申)
病老人之长子出亡适他国。六年不归。而使其病亲嗟思不已。至今次子搜访不得。而身先毙焉。则其所谓长子者。诚不孝之大者也。所当不以长子处之也。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6L 页
 又何以几千里他国某处在之涂说为准。而经岁不葬其亲耶。当速卜日安葬。而凡馈奠拜宾。主人虞卒祔等礼。当以次子摄事。以待长子归日。恐是不得已之权行也。次子既以亲命访兄不逢。而独归于其亲已没之后而行此权摄之事。则前后事状。不可不备悉告达于灵筵也。告辞在下。
又何以几千里他国某处在之涂说为准。而经岁不葬其亲耶。当速卜日安葬。而凡馈奠拜宾。主人虞卒祔等礼。当以次子摄事。以待长子归日。恐是不得已之权行也。次子既以亲命访兄不逢。而独归于其亲已没之后而行此权摄之事。则前后事状。不可不备悉告达于灵筵也。告辞在下。不肖某去某月。奉承府君命令。遍访伯兄于海参。莫知所向。故去某月某日。独自归来。则府君已于某月某日下世矣。扣地号天。益增罔极。按礼士踰月而葬。则府君葬事。当从士礼也。而踰此期者。不肖未归之故也。及其归来。即当安葬矣。但闻涂说。则伯兄在某处云。故拟将待春更访归来然后完窆伏计。而问于礼家。则曰待出亡他国。多年未归之游子。而经岁不葬其亲者。恐非情礼云云。今据此说。将欲行葬。今已得地于某郡某里某坐之原。将以某月某日襄奉。而自主人赠以后事。不肖当摄主举行。以待伯兄归来。敢告。
铭旌本为尸柩而设。故旌柩元不相离。则虽于藁殡。置铭旌于柩上。此亦似有先儒说而姑不记忆矣。今失旌柩不相离之本意而旌不随柩。则不得已而待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7H 页
 完窆时而揭之柩前恐当。
完窆时而揭之柩前恐当。次子摄主则题主祝年月日下。当曰孤子某出亡未归。支子某摄事。敢昭告于云云。虞卒哭祝辞亦然。小大祥则改孤子为孝子。
次子闻丧。在于丧出六朔后归家之日。则当以是日为除丧之期。小大祥祭则依丧服小记祭不为除丧之说。备三献行之恐当。
若出亡之长子来归于小大祥垂毕之时。则当依齐仆射王俭论。恐为得正。齐高祖皇太子妃薨。皇孙闻喜王在远承凶于丧后一月。而仆射王俭曰。闻喜王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期。灵筵祭奠。当随在家人。再期而毁。
与孙承敏(壬辰)
汝之今行。非但为往见妇之父母也。汝于在家。自不免小小役事。无益于事而惟放心肆志。无限心术之害。不可形言。故全为读书一事。教汝有今行。不须多言。静室危坐。昼夜通读其乡约与小学。期令成诵。勿须贪多。一日只受八九行读之。而又于小閒隙时。虽以秃笔时时习字于粉板上。字必楷正也。书是六艺中一艺。而书以观心画。而况万古心迹。皆因书传世。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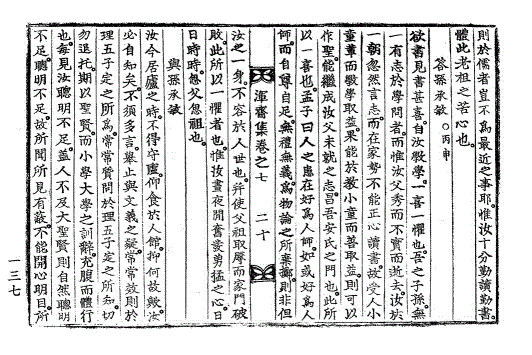 则于儒者岂不为最近之事耶。惟汝十分勤读勤书。体此老祖之苦心也。
则于儒者岂不为最近之事耶。惟汝十分勤读勤书。体此老祖之苦心也。答孙承敏(丙申)
欲书见书甚喜。自汝敩学。一喜一惧也。吾之子孙。无一有志于学问者。而惟汝父秀而不实而逝去。汝于一朝忽然言志。而在家势不能正心读书。故受人小童辈而敩学取益。果能于教小童而善取益。则可以作圣。能继成汝父未就之志。昌吾安氏之门也。此所以一喜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如或好为人师。而自尊自足。无礼无义。为物论之所弃掷。则非但汝之一身。不容于人世也。并使父祖取辱而家门破败。此所以一惧者也。惟汝昼夜閒奋发勇猛之心。日日时时。思父思祖也。
与孙承敏
汝今居庐之时。不得守庐。仰食于人馆。抑何故欤。汝必自知矣。不须多言。举止与文义之疑。常常效则于理五子定之所为。常常质问于理五子定之所知。切勿退托。期以圣贤。而小学大学之训辞。充腹而体行也。每见汝聪明不足。盖人不及大圣贤则自然聪明不足。聪明不足。故所闻所见有蔽。不能开心明目。所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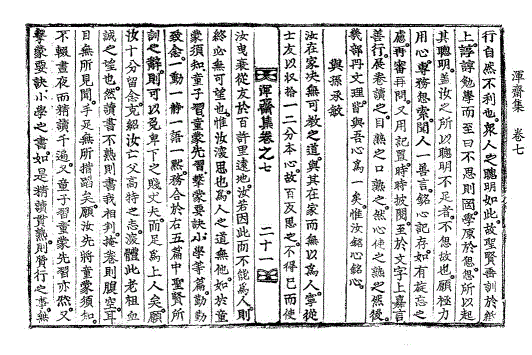 行自然不利也。众人之聪明如此。故圣贤垂训于纸上。谆谆勉学而至曰不思则罔。学原于思。思所以起其聪明。盖汝之所以聪明不足者。不思故也。愿极力用心。专务思索。闻人一善言。铭心记存。如有旋忘之虑。再审再问。又用记置。时时披阅。至于文字上嘉言善行。展卷读之。目熟之口熟之。然心使之熟之然后。几部册文理。皆与吾心为一矣。惟汝铭心铭心。
行自然不利也。众人之聪明如此。故圣贤垂训于纸上。谆谆勉学而至曰不思则罔。学原于思。思所以起其聪明。盖汝之所以聪明不足者。不思故也。愿极力用心。专务思索。闻人一善言。铭心记存。如有旋忘之虑。再审再问。又用记置。时时披阅。至于文字上嘉言善行。展卷读之。目熟之口熟之。然心使之熟之然后。几部册文理。皆与吾心为一矣。惟汝铭心铭心。与孙承敏
汝在家决无可教之道。与其在家而无以为人。宁从士友以收拾一二分本心。故百反思之。不得已而使汝曳衰从友于百许里远地。汝若因此而不能为人。则终必无可望也。惟汝深思也。为人之道无他。如于童蒙须知,童子习,童蒙先习,击蒙要诀,小学等篇。勤勤致念。一动一静一语一默。务合于右五篇中圣贤所训之辞。则可以免卑下之贱丈夫。而足为上人矣。愿汝十分留念。克绍汝亡父高特之志。深体此老祖血诚之望也。然读书不熟则书我相判。掩卷则腹空。耳目无所见闻。手足无所措蹈矣。愿汝先将童蒙须知。不辍昼夜而精读千遍。又童子习,童蒙先习亦然。又击蒙要诀,小学之书。如是精读贯熟。则质行之事。无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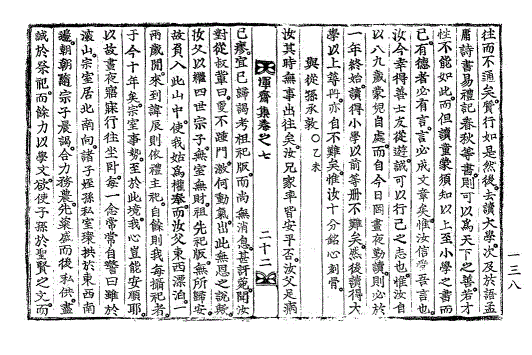 往而不通矣。质行如是然后。去读大学。次及于语孟庸诗书易礼记春秋等书。则可以为天下之善。若才性不能如此。而但读童蒙须知以上至小学之书而已。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成文章矣。惟汝信受吾言也。汝今幸得善士友从游。诚可以行己之志也。惟汝自以八九岁蒙儿自处。而自今日罔昼夜勤读。则必于一年终始。读得小学以前等册不难矣。然后读得大学以上筑册。亦自不难矣。惟汝十分铭心刻骨。
往而不通矣。质行如是然后。去读大学。次及于语孟庸诗书易礼记春秋等书。则可以为天下之善。若才性不能如此。而但读童蒙须知以上至小学之书而已。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成文章矣。惟汝信受吾言也。汝今幸得善士友从游。诚可以行己之志也。惟汝自以八九岁蒙儿自处。而自今日罔昼夜勤读。则必于一年终始。读得小学以前等册不难矣。然后读得大学以上筑册。亦自不难矣。惟汝十分铭心刻骨。与从孙承敦(乙未)
汝其时无事出往矣。汝兄家率皆安平否。汝父足病已瘳。宜已归谒考祖祀版。而尚无消息。甚讶菀。闻汝对从叔辈曰。更不踵门。激何动气。出此无恩之说欤。汝父以继四世宗子。无室无财。祖先祀版。无所归安。故负入此山中。使我姑为权奉。而汝父东西漂泊。一两岁閒。来到讳辰则依礼主祀。自馀则我每摄祀者。于今十年矣。宗室事势。至于此境。我心岂能安顺耶。以故昼夜寤寐行往坐卧。每一念常常自警曰虽于深山。宗室居北南向。诸子侄孙私室环拱于东西南边。朝朝随宗子晨谒。合力务农。先粢盛而后私供。尽诚于祭祀。而馀力以学文。欲使子孙于圣贤之文。而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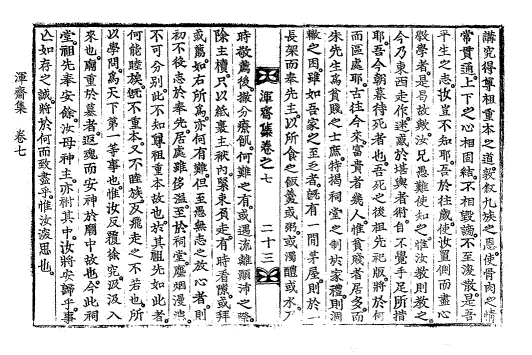 讲究得尊祖重本之道。敦叙九族之恩。使骨肉之情常贯通。上下之心相固结。不相毁谤。不至涣散。是吾平生之志。汝岂不知耶。吾于往岁。使汝置侧而尽心敩学者。是曷故欤。汝兄愚难使知之。惟汝教则教之。今乃东西走作。迷惑于堪舆者术。自不觉手足所措耶。吾今朝暮待死者也。吾死之后祖先祀版。将于何而区处耶。古往今来。富贵者几人。惟贫贱者居多。而朱先生为贫贱之士庶。特揭祠堂之制于家礼。则涸辙之困。虽如吾家之至乏者。既有一閒茅屋。则于一长架而奉先主。以所食之饭羹或粥。或浊醴或水。及时敬荐后。撤分疗饥。何难之有。或遇流离颠沛之际。除主椟。只以纸裹主袱内。紧束负走。有时看隙。或拜或荐。如右所为。亦何有难。但至愚无志之放心者。则初不役志于奉先。居处虽侈溢。至于祠堂。尘烟漫漶。不可分别。此不知尊祖重本故也。于其祖先如此者。何能睦族。既不重本。又不睦族。反飞走之不若也。所以学问。为天下第一等事也。惟汝反覆徐究。汲汲入来也。庙重于墓者。返魂而安神于庙中故也。今此祠堂。祖先奉安馀。汝母神主。亦祔其中。汝将安归乎。事亡如存之诚。将于何而致尽乎。惟汝深思也。
讲究得尊祖重本之道。敦叙九族之恩。使骨肉之情常贯通。上下之心相固结。不相毁谤。不至涣散。是吾平生之志。汝岂不知耶。吾于往岁。使汝置侧而尽心敩学者。是曷故欤。汝兄愚难使知之。惟汝教则教之。今乃东西走作。迷惑于堪舆者术。自不觉手足所措耶。吾今朝暮待死者也。吾死之后祖先祀版。将于何而区处耶。古往今来。富贵者几人。惟贫贱者居多。而朱先生为贫贱之士庶。特揭祠堂之制于家礼。则涸辙之困。虽如吾家之至乏者。既有一閒茅屋。则于一长架而奉先主。以所食之饭羹或粥。或浊醴或水。及时敬荐后。撤分疗饥。何难之有。或遇流离颠沛之际。除主椟。只以纸裹主袱内。紧束负走。有时看隙。或拜或荐。如右所为。亦何有难。但至愚无志之放心者。则初不役志于奉先。居处虽侈溢。至于祠堂。尘烟漫漶。不可分别。此不知尊祖重本故也。于其祖先如此者。何能睦族。既不重本。又不睦族。反飞走之不若也。所以学问。为天下第一等事也。惟汝反覆徐究。汲汲入来也。庙重于墓者。返魂而安神于庙中故也。今此祠堂。祖先奉安馀。汝母神主。亦祔其中。汝将安归乎。事亡如存之诚。将于何而致尽乎。惟汝深思也。浑斋集卷之七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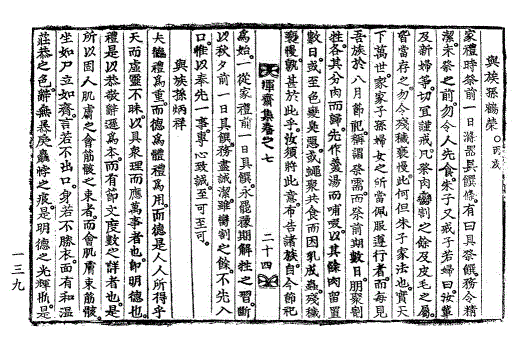 与族孙鹤荣(丙戌)
与族孙鹤荣(丙戌)家礼时祭前一日涤器具馔条。有曰具祭馔。务令精洁。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朱子又戒子若妇曰。汝辈及新妇等。切宜谨戒。凡祭肉脔割之馀及皮毛之属。皆当存之。勿令残秽亵慢。此何但朱子家法也。实天下万世。家家子孙妇女之所当佩服遵行者。而每见吾族于八月节祀。称谓祭需。而祭前期数日。朋聚割牲。各其分肉而归。先作羹汤而哺啜。以其馀肉留置数日。或至色变臭恶。或蝇聚共食而因乳成虫。残秽亵慢。孰甚于此乎。汝须将此意。布告诸族。自今节祀为始。一从家礼前一日具馔。永罢豫期解牲之习。断以秋夕前一日具馔。务尽诚洁。虽脔割之馀。不先入口。惟以奉先一事。专心致诚。至可至可。
与族孙炳祥
夫德礼为重。而德为体礼为用。而德是人人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即明德也。礼是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者也。是所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者。而会肌肤束筋骸。坐如尸立如齐。言若不出口。身若不胜衣。面有和温庄恭之色。辞无暴戾粗悖之痕。是明德之光辉也。是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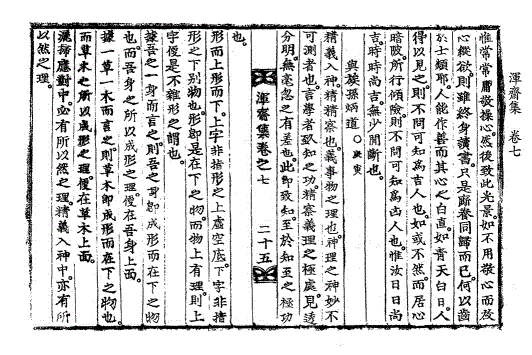 惟常常庸敬操心。然后致此光景。如不用敬心而放心纵欲。则虽终身读书。只是厮养同归而已。何以齿于士类耶。人能作善而其心之白直。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见之。则不问可知为吉人也。如或不然。而居心暗陂。所行倾险。则不问可知为凶人也。惟汝日日尚吉。时时尚吉。无少閒断也。
惟常常庸敬操心。然后致此光景。如不用敬心而放心纵欲。则虽终身读书。只是厮养同归而已。何以齿于士类耶。人能作善而其心之白直。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见之。则不问可知为吉人也。如或不然。而居心暗陂。所行倾险。则不问可知为凶人也。惟汝日日尚吉。时时尚吉。无少閒断也。与族孙炳道(庚寅)
精义入神。精精察也。义事物之理也。神理之神妙不可测者也。言学者致知之功。精察义理之极处。见透分明。无毫忽之有差也。此即致知。至于知至之极功也。
形而上形而下。上字非指形之上虚空底。下字非指形之下别物也。形即是在下之物。而物上有理。则上字便是不杂形之谓也。
据吾之一身而言之。则吾之身即成形而在下之物也。而吾身之所以成形之理。便在吾身上面。
据一草一木而言之。则草木即成形而在下之物也。而草木之所以成形之理。便在草木上面。
洒扫应对中。必有所以然之理。精义入神中。亦有所以然之理。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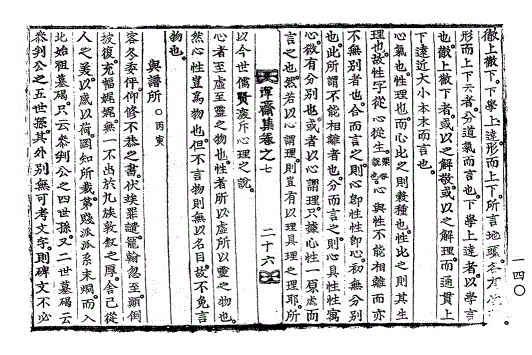 彻上彻下。下学上达。形而上下。所言地头。各有▦▦。形而上下云者。分道气而言也。下学上达者。以学言也。彻上彻下者。或以之解敬。或以之解理。而通贯上下远近大小本末而言也。
彻上彻下。下学上达。形而上下。所言地头。各有▦▦。形而上下云者。分道气而言也。下学上达者。以学言也。彻上彻下者。或以之解敬。或以之解理。而通贯上下远近大小本末而言也。心气也。性理也。而心比之则谷种也。性比之则其生理也。故性字从心从生。(栗谷说也。)心与性不能相离而亦不无别者也。合而言之。则心即性性即心。初无分别也。此所谓不能相离者也。分而言之。则心具性性寓心。微有分别也。或者以心谓理。只据心性一原处而言之也。然若以心谓理。则岂有以理具理之理耶。所以今世儒贤深斥心理之说。
心者至虚至灵之物也。性者所以虚所以灵之物也。然心性岂为物也。但不言物则无以名目。故不免言物也。
与谱所(丙寅)
客冬委伻。仰修不恭之书。伏俟罪谴。宠翰忽至。颠倒披复。充幅娓娓。无一不出于九族敦叙之厚。舍己从人之美。以感以荷。罔知所裁。第贱派派系末烱。而入北始祖墓碣。只云参判公之四世孙。又二世墓碣云参判公之五世孙。其外别无可考文字。则碑文不必
浑斋集卷之七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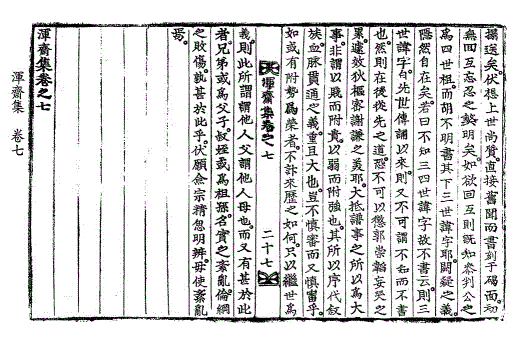 拓送矣。伏想上世尚质。直接旧闻而书刻于碣面。初无回互忘忍之弊明矣。如欲回互则既知参判公之为四世祖。而胡不明书其下三世讳字耶。阙疑之义。隐然自在矣。若曰不知三四世讳字故不书云。则三世讳字。自先世传诵以来。则又不可谓不知而不书也。然则在后从先之道。恐不可以惩郭崇韬妄哭之累。遽效狄枢密谢谦之美耶。大抵谱事之所以为大事。非谓以贱而附贵。以弱而附强也。其所以序代叙族。血脉贯通之义。重且大也。岂不慎审而又慎审乎。如或有附势为荣者。不计来历之如何。只以继世为义。则此所谓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也。而又有甚于此者。兄弟或为父子。叔侄或为祖孙。名实之紊乱。伦纲之败伤。孰甚于此乎。伏愿佥宗精思明辨。毋使紊乱焉。
拓送矣。伏想上世尚质。直接旧闻而书刻于碣面。初无回互忘忍之弊明矣。如欲回互则既知参判公之为四世祖。而胡不明书其下三世讳字耶。阙疑之义。隐然自在矣。若曰不知三四世讳字故不书云。则三世讳字。自先世传诵以来。则又不可谓不知而不书也。然则在后从先之道。恐不可以惩郭崇韬妄哭之累。遽效狄枢密谢谦之美耶。大抵谱事之所以为大事。非谓以贱而附贵。以弱而附强也。其所以序代叙族。血脉贯通之义。重且大也。岂不慎审而又慎审乎。如或有附势为荣者。不计来历之如何。只以继世为义。则此所谓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也。而又有甚于此者。兄弟或为父子。叔侄或为祖孙。名实之紊乱。伦纲之败伤。孰甚于此乎。伏愿佥宗精思明辨。毋使紊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