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x 页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启
启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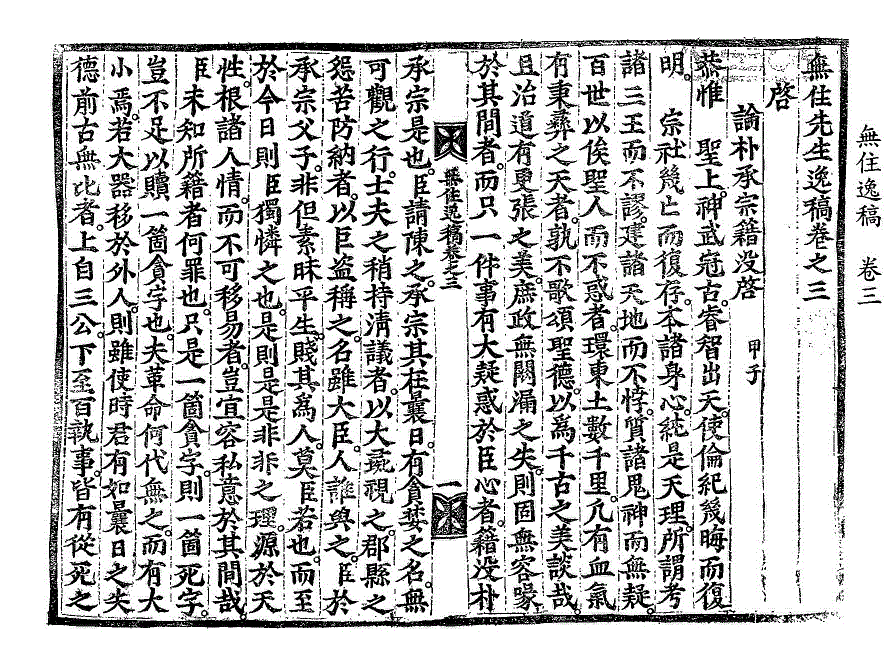 论朴承宗籍没启(甲子)
论朴承宗籍没启(甲子)恭惟 圣上。神武冠古。睿智出天。使伦纪几晦而复明。 宗社几亡而复存。本诸身心。纯是天理。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环东土数千里。凡有血气有秉彝之天者。孰不歌颂圣德。以为千古之美谈哉。且治道有更张之美。庶政无阙漏之失。则固无容喙于其间者。而只一件事有大疑惑于臣心者。籍没朴承宗是也。臣请陈之。承宗其在曩日。有贪婪之名。无可观之行。士夫之稍持清议者。以大彘视之。郡县之怨苦防纳者。以巨盗称之。名虽大臣。人谁与之。臣于承宗父子。非但素昧平生。贱其为人。莫臣若也。而至于今日则臣独怜之也。是则是是非非之理。源于天性。根诸人情。而不可移易者。岂宜容私意于其间哉。臣未知所籍者何罪也。只是一个贪字。则一个死字。岂不足以赎一个贪字也。夫革命何代无之。而有大小焉。若大器移于外人。则虽使时君有如曩日之失德前古无比者。上自三公。下至百执事。皆有从死之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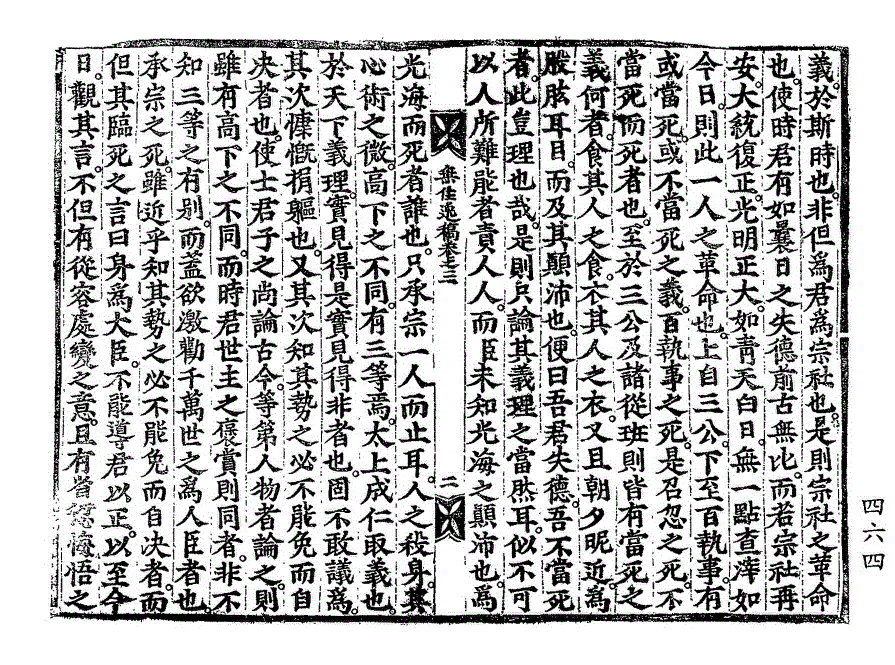 义。于斯时也。非但为君为宗社也。是则宗社之革命也。使时君有如曩日之失德前古无比。而若宗社再安。大统复正。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无一点查滓如今日。则此一人之革命也。上自三公。下至百执事。有或当死。或不当死之义。百执事之死。是召忽之死。不当死而死者也。至于三公及诸从班则皆有当死之义何者。食其人之食。衣其人之衣。又且朝夕昵近。为股肱耳目。而及其颠沛也。便曰吾君失德。吾不当死者。此岂理也哉。是则只论其义理之当然耳。似不可以人所难能者责人人。而臣未知光海之颠沛也。为光海而死者谁也。只承宗一人而止耳。人之杀身。其心术之微。高下之不同。有三等焉。太上成仁取义也。于天下义理。实见得是实见得非者也。固不敢议为。其次慷慨捐躯也。又其次知其势之必不能免而自决者也。使士君子之尚论古今。等第人物者论之。则虽有高下之不同。而时君世主之褒赏则同者。非不知三等之有别。而盖欲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者也。承宗之死。虽近乎知其势之必不能免而自决者。而但其临死之言曰身为大臣。不能导君以正。以至今日。观其言。不但有从容处变之意。且有省愆悔悟之
义。于斯时也。非但为君为宗社也。是则宗社之革命也。使时君有如曩日之失德前古无比。而若宗社再安。大统复正。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无一点查滓如今日。则此一人之革命也。上自三公。下至百执事。有或当死。或不当死之义。百执事之死。是召忽之死。不当死而死者也。至于三公及诸从班则皆有当死之义何者。食其人之食。衣其人之衣。又且朝夕昵近。为股肱耳目。而及其颠沛也。便曰吾君失德。吾不当死者。此岂理也哉。是则只论其义理之当然耳。似不可以人所难能者责人人。而臣未知光海之颠沛也。为光海而死者谁也。只承宗一人而止耳。人之杀身。其心术之微。高下之不同。有三等焉。太上成仁取义也。于天下义理。实见得是实见得非者也。固不敢议为。其次慷慨捐躯也。又其次知其势之必不能免而自决者也。使士君子之尚论古今。等第人物者论之。则虽有高下之不同。而时君世主之褒赏则同者。非不知三等之有别。而盖欲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者也。承宗之死。虽近乎知其势之必不能免而自决者。而但其临死之言曰身为大臣。不能导君以正。以至今日。观其言。不但有从容处变之意。且有省愆悔悟之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5H 页
 端。不亦悲乎。其在平时。以经明行粹名于世。而及其颠沛。不能舍躯命于造次俄顷之间。贻讥于千载之下者。古今天下何限。而承宗以一鄙夫。当死而死。不亦奇乎。 即真之初。臣意以为承宗必蒙褒赏之典。岂意有籍没之命也。臣思而又思。百思千思。未知其所以然也。久而复思之。则固知 殿下必以为承宗之婢仆。出于民也。承宗之田宅。出于民也。承宗之金帛。出于民也。出于民者没于官。则有以慰万姓怨苦之心。而快一时之耳目也。是则 殿下之为此举。诚出寻常万万。而然而 殿下徒知其快一时之耳目。而不暇计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者也。且不廉君子之大过。而凡人则无怪。昭代之大罪而曩日则常事。 殿下知其此义。故曩日之或以不廉名者。举皆容于包荒之中。而独承宗未蒙宥赦之典。不亦冤乎。圣帝明王之御天下也。一视同仁。奉三无私。其于刑政。无有内外。无有亲疏。无有远近。无间生死。而 殿下则何其厚于生者而薄于死者乎。臣窃怪之。易曰遏恶扬善。帝舜之德。万善俱备。而子思于中庸。称舜之德。只举其隐恶扬善。 殿下今日当以帝舜为法。则其于承宗。所当隐前日之恶。而扬今日之善也。臣愚
端。不亦悲乎。其在平时。以经明行粹名于世。而及其颠沛。不能舍躯命于造次俄顷之间。贻讥于千载之下者。古今天下何限。而承宗以一鄙夫。当死而死。不亦奇乎。 即真之初。臣意以为承宗必蒙褒赏之典。岂意有籍没之命也。臣思而又思。百思千思。未知其所以然也。久而复思之。则固知 殿下必以为承宗之婢仆。出于民也。承宗之田宅。出于民也。承宗之金帛。出于民也。出于民者没于官。则有以慰万姓怨苦之心。而快一时之耳目也。是则 殿下之为此举。诚出寻常万万。而然而 殿下徒知其快一时之耳目。而不暇计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者也。且不廉君子之大过。而凡人则无怪。昭代之大罪而曩日则常事。 殿下知其此义。故曩日之或以不廉名者。举皆容于包荒之中。而独承宗未蒙宥赦之典。不亦冤乎。圣帝明王之御天下也。一视同仁。奉三无私。其于刑政。无有内外。无有亲疏。无有远近。无间生死。而 殿下则何其厚于生者而薄于死者乎。臣窃怪之。易曰遏恶扬善。帝舜之德。万善俱备。而子思于中庸。称舜之德。只举其隐恶扬善。 殿下今日当以帝舜为法。则其于承宗。所当隐前日之恶。而扬今日之善也。臣愚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5L 页
 以为 殿下既以籍没。罚承宗曩日之罪。慰万姓之心。而快一时之耳目。又以还给赏承宗临死之善。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则此所谓罚一人而千万人惧。赏一人而千万人劝者也。此是 殿下操风化。抑扬进退鼓舞振作之良法也。使士大夫之稍持行检者。咸曰承宗从君于昏。只以纳贿为事。而毕竟以一个死字。蒙 昭代之褒赏。吾辈素以廉耻自许。而何后于承宗哉。争自奋发。砥砺名节。则是使为善者。益进于善也。使士大夫之素无行检者。咸曰承宗从君于昏。只以纳贿为事。而毕竟以一个死字。蒙 昭代之褒赏。吾辈虽无以名节著称。而若一为善。亦一承宗耳。争自饬躬。革面改行。则是使为恶者。兴起于为善也。赏罚一人。而使善恶皆有劝。其于治道。岂无小补哉。不然则臣恐 殿下此举。遏人人为善之路。而非所以示法于后世子孙者也。告 启之辞。当尚简切。而臣则语无伦理。文且重复。固知不宜达于 四聪之下。而然且不知止者。文若率略则盖恐 殿下不留睿念耳。臣在岭外。固欲以疏章因县道陈之。而但念思不出位。易象所美。越职言事。古人所戒。兹敢嗫嚅以待时月。即今幸蒙 恩除。身在言地。其敢含嘿
以为 殿下既以籍没。罚承宗曩日之罪。慰万姓之心。而快一时之耳目。又以还给赏承宗临死之善。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则此所谓罚一人而千万人惧。赏一人而千万人劝者也。此是 殿下操风化。抑扬进退鼓舞振作之良法也。使士大夫之稍持行检者。咸曰承宗从君于昏。只以纳贿为事。而毕竟以一个死字。蒙 昭代之褒赏。吾辈素以廉耻自许。而何后于承宗哉。争自奋发。砥砺名节。则是使为善者。益进于善也。使士大夫之素无行检者。咸曰承宗从君于昏。只以纳贿为事。而毕竟以一个死字。蒙 昭代之褒赏。吾辈虽无以名节著称。而若一为善。亦一承宗耳。争自饬躬。革面改行。则是使为恶者。兴起于为善也。赏罚一人。而使善恶皆有劝。其于治道。岂无小补哉。不然则臣恐 殿下此举。遏人人为善之路。而非所以示法于后世子孙者也。告 启之辞。当尚简切。而臣则语无伦理。文且重复。固知不宜达于 四聪之下。而然且不知止者。文若率略则盖恐 殿下不留睿念耳。臣在岭外。固欲以疏章因县道陈之。而但念思不出位。易象所美。越职言事。古人所戒。兹敢嗫嚅以待时月。即今幸蒙 恩除。身在言地。其敢含嘿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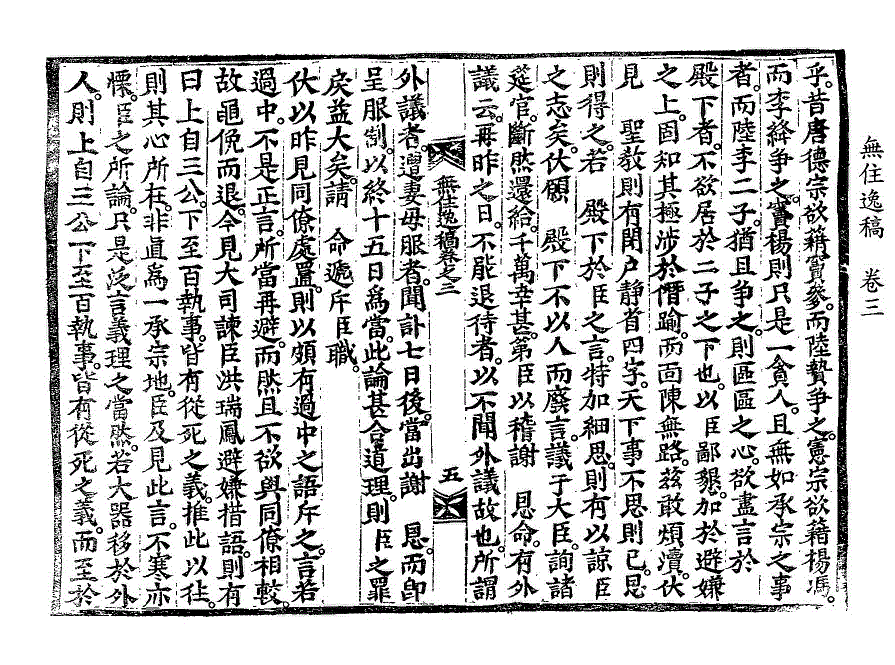 乎。昔唐德宗欲籍窦参。而陆贽争之。宪宗欲籍杨冯。而李绛争之。窦杨则只是一贪人。且无如承宗之事者。而陆李二子。犹且争之。则区区之心。欲尽言于 殿下者。不欲居于二子之下也。以臣鄙恳。加于避嫌之上。固知其极涉于僭踰。而面陈无路。兹敢烦渎。伏见 圣教则有闭户静省四字。天下事不思则已。思则得之。若 殿下于臣之言。特加细思。则有以谅臣之志矣。伏愿 殿下不以人而废言。议于大臣。询诸筵官。断然还给。千万幸甚。第臣以稽谢 恩命。有外议云。再昨之日。不能退待者。以不闻外议故也。所谓外议者。遭妻母服者。闻讣七日后。当出谢 恩。而即呈服制。以终十五日为当。此论甚合道理。则臣之罪戾益大矣。请 命递斥臣职。
乎。昔唐德宗欲籍窦参。而陆贽争之。宪宗欲籍杨冯。而李绛争之。窦杨则只是一贪人。且无如承宗之事者。而陆李二子。犹且争之。则区区之心。欲尽言于 殿下者。不欲居于二子之下也。以臣鄙恳。加于避嫌之上。固知其极涉于僭踰。而面陈无路。兹敢烦渎。伏见 圣教则有闭户静省四字。天下事不思则已。思则得之。若 殿下于臣之言。特加细思。则有以谅臣之志矣。伏愿 殿下不以人而废言。议于大臣。询诸筵官。断然还给。千万幸甚。第臣以稽谢 恩命。有外议云。再昨之日。不能退待者。以不闻外议故也。所谓外议者。遭妻母服者。闻讣七日后。当出谢 恩。而即呈服制。以终十五日为当。此论甚合道理。则臣之罪戾益大矣。请 命递斥臣职。伏以昨见同僚处置。则以颇有过中之语斥之。言若过中。不是正言。所当再避。而然且不欲与同僚相较。故黾俛而退。今见大司谏臣洪瑞凤避嫌措语。则有曰上自三公。下至百执事。皆有从死之义。推此以往。则其心所在。非直为一承宗地。臣及见此言。不寒亦慄。臣之所论。只是泛言义理之当然。若大器移于外人。则上自三公下至百执事。皆有从死之义。而至于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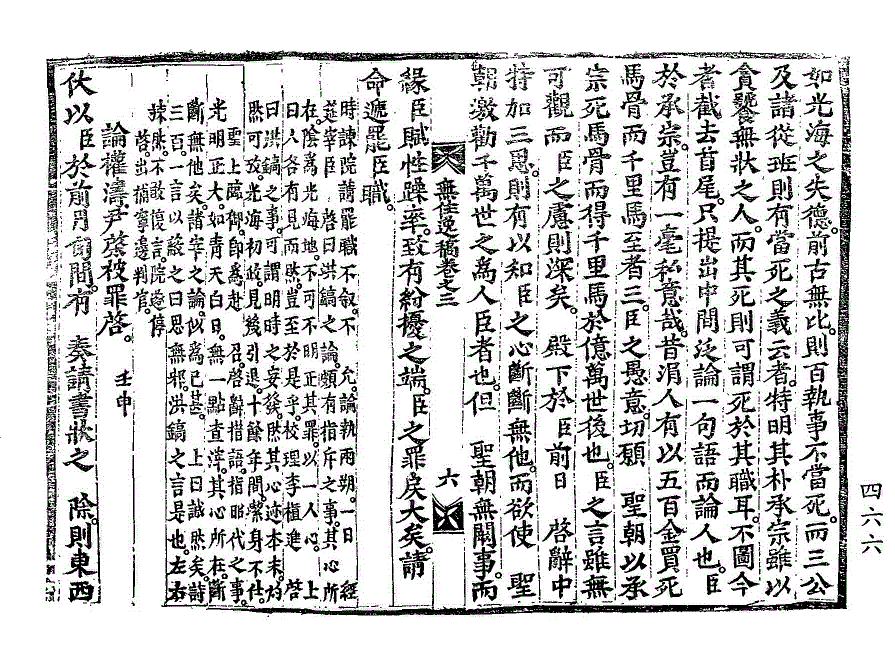 如光海之失德。前古无比。则百执事不当死。而三公及诸从班则有当死之义云者。特明其朴承宗虽以贪饕无状之人。而其死则可谓死于其职耳。不图今者截去首尾。只提出中间泛论一句语而论人也。臣于承宗。岂有一毫私意哉。昔涓人有以五百金买死马骨而千里马至者三。臣之愚意。切愿 圣朝以承宗死马骨而得千里马于亿万世后也。臣之言虽无可观而臣之虑则深矣。 殿下于臣前日 启辞中特加三思。则有以知臣之心断断无他。而欲使 圣朝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者也。但 圣朝无阙事。而缘臣赋性躁率。致有纷扰之端。臣之罪戾大矣。请 命递罢臣职。
如光海之失德。前古无比。则百执事不当死。而三公及诸从班则有当死之义云者。特明其朴承宗虽以贪饕无状之人。而其死则可谓死于其职耳。不图今者截去首尾。只提出中间泛论一句语而论人也。臣于承宗。岂有一毫私意哉。昔涓人有以五百金买死马骨而千里马至者三。臣之愚意。切愿 圣朝以承宗死马骨而得千里马于亿万世后也。臣之言虽无可观而臣之虑则深矣。 殿下于臣前日 启辞中特加三思。则有以知臣之心断断无他。而欲使 圣朝激劝千万世之为人臣者也。但 圣朝无阙事。而缘臣赋性躁率。致有纷扰之端。臣之罪戾大矣。请 命递罢臣职。(时谏院请罢职不叙。不 允。论执两朔。一日 经筵宰臣 启曰洪镐之论。颇有指斥之事。其心所在。阴为光海地。不可不明正其罪。以一人心。 上曰人各有见而然。岂至于是乎。校理李植进 启曰洪镐之事。可谓明时之妄发。然其心迹本末。灼然可考。光海初政。见几引退。十馀年间。洁身不仕。 圣上临御。即为赴 召。启辞措语。指昭代之事。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无一点查滓。其心所在。断断无他矣。诸宰之论。似为已甚。 上曰诚然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洪镐之言是也。左右竦然。不敢复言。院遂停 启。出补宁边判官。)
论权涛,尹棨被罪启。(壬申)
伏以臣于前月旬间。有 奏请书状之 除。则东西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7H 页
 南北。惟 命之从。所当趁时登程来谢。以免逋慢之罪。而缘臣重患风痹。针灸诸穴。疮未完合。调理半月。晦初始得踰岭。行到忠原。祇受本职之 命。自惟臣之无状。最出人下。而何获蒙误 恩至于此极哉。诚惶诚感。罔知所措。路次得见之。乃宪吏所传朝报。而其中一二款。乃权涛远窜及尹棨等削黜事也。私自语曰何我 圣上之当此大礼已定之日。而必罪言官也。心窃怪之。及到江上闻之。则涛有南海之行。棨亦未免削黜。而多官已停 启矣。停 启有日。则虽似既往。而但臣则自远来。恶得无言。 圣上称棨以作威胁人。则其于原情定罪。太不近似。而然不至为蛮烟瘴雨之人。则臣姑置之。举其重者而论之。涛之所言。虽曰明时之妄发。只是国人之云云。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有是心而不敢发焉者也。岂涛之私言哉。若以三代以上。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观之。则谥字之必多。恐非古先哲王之令典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今涛之言。必逆乎 圣上之心矣。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今涛之言。必违乎 圣上之意矣。传曰心有所忿𢜀则不得其正。 圣上必以涛
南北。惟 命之从。所当趁时登程来谢。以免逋慢之罪。而缘臣重患风痹。针灸诸穴。疮未完合。调理半月。晦初始得踰岭。行到忠原。祇受本职之 命。自惟臣之无状。最出人下。而何获蒙误 恩至于此极哉。诚惶诚感。罔知所措。路次得见之。乃宪吏所传朝报。而其中一二款。乃权涛远窜及尹棨等削黜事也。私自语曰何我 圣上之当此大礼已定之日。而必罪言官也。心窃怪之。及到江上闻之。则涛有南海之行。棨亦未免削黜。而多官已停 启矣。停 启有日。则虽似既往。而但臣则自远来。恶得无言。 圣上称棨以作威胁人。则其于原情定罪。太不近似。而然不至为蛮烟瘴雨之人。则臣姑置之。举其重者而论之。涛之所言。虽曰明时之妄发。只是国人之云云。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有是心而不敢发焉者也。岂涛之私言哉。若以三代以上。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观之。则谥字之必多。恐非古先哲王之令典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今涛之言。必逆乎 圣上之心矣。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今涛之言。必违乎 圣上之意矣。传曰心有所忿𢜀则不得其正。 圣上必以涛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7L 页
 之言。有所忿𢜀矣。 圣上何不于此等文字。咀嚼详味。虚心而观理乎。臣窃以为 圣上于学问思辨之功。有所未至也。幺么一权涛。得美名于千载之下。而使 圣上终归于拒谏自用之地。则殊非一国臣民所望于今日者也。多官虽论执累年。必回 天听而后已者。乃是言责。而遽尔停 启。臣所未晓也。臣安肯私庇权涛。而有一毫欺罔之心哉。 圣上若因臣之言。而追回岭海之臣。则 圣上之包荒大度。当高出百王。而朝廷之上。必多有不欺犯颜之人矣。臣唯思奉行文书之任。完了使事于万里之外。而不知其他。适千万意外。叨此言地。此臣之所以不得不陈者也。第臣来时不但著艾未久。不便跨马。且近将赴京。随行甚多。故不得不借船下来。而到此闻之则台官之往来于水路。为近日之大禁云。臣之不察之失大矣。请 命递差臣职。
之言。有所忿𢜀矣。 圣上何不于此等文字。咀嚼详味。虚心而观理乎。臣窃以为 圣上于学问思辨之功。有所未至也。幺么一权涛。得美名于千载之下。而使 圣上终归于拒谏自用之地。则殊非一国臣民所望于今日者也。多官虽论执累年。必回 天听而后已者。乃是言责。而遽尔停 启。臣所未晓也。臣安肯私庇权涛。而有一毫欺罔之心哉。 圣上若因臣之言。而追回岭海之臣。则 圣上之包荒大度。当高出百王。而朝廷之上。必多有不欺犯颜之人矣。臣唯思奉行文书之任。完了使事于万里之外。而不知其他。适千万意外。叨此言地。此臣之所以不得不陈者也。第臣来时不但著艾未久。不便跨马。且近将赴京。随行甚多。故不得不借船下来。而到此闻之则台官之往来于水路。为近日之大禁云。臣之不察之失大矣。请 命递差臣职。进前疏启(癸未)
启曰臣前以参议待罪骑省之日。略陈鍊兵之方。盖令各道各邑劝诱编伍。炮手私备铳药丸。使之私习。期至成材。以为缓急之用也。古之人进说于其君也。虽被峻郤。以至裂纸而投于地。而徐拾而补之后。进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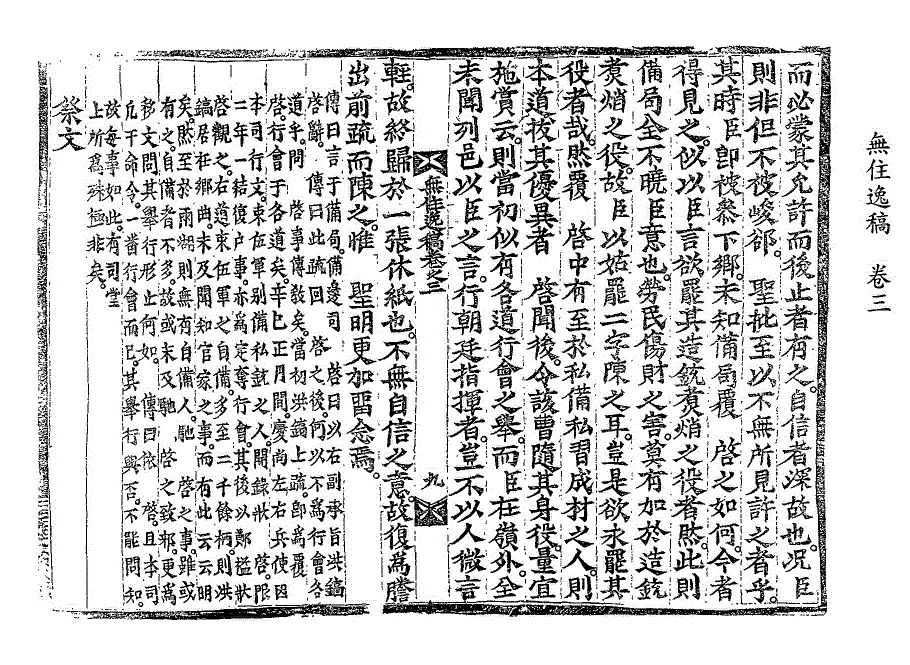 而必蒙其允许而后止者有之。自信者深故也。况臣则非但不被峻郤。 圣批至以不无所见许之者乎。其时臣即被参下乡。未知备局覆 启之如何。今者得见之。似以臣言欲罢其造铳煮焇之役者然。此则备局全不晓臣意也。劳民伤财之害。莫有加于造铳煮焇之役。故臣以姑罢二字陈之耳。岂是欲永罢其役者哉。然覆 启中有至于私备私习成材之人。则本道拔其优异者 启闻后。令该曹随其身役。量宜施赏云。则当初似有各道行会之举。而臣在岭外。全未闻列邑以臣之言。行朝廷指挥者。岂不以人微言轻。故终归于一张休纸也。不无自信之意。故复为誊出前疏而陈之。惟 圣明更加留念焉。
而必蒙其允许而后止者有之。自信者深故也。况臣则非但不被峻郤。 圣批至以不无所见许之者乎。其时臣即被参下乡。未知备局覆 启之如何。今者得见之。似以臣言欲罢其造铳煮焇之役者然。此则备局全不晓臣意也。劳民伤财之害。莫有加于造铳煮焇之役。故臣以姑罢二字陈之耳。岂是欲永罢其役者哉。然覆 启中有至于私备私习成材之人。则本道拔其优异者 启闻后。令该曹随其身役。量宜施赏云。则当初似有各道行会之举。而臣在岭外。全未闻列邑以臣之言。行朝廷指挥者。岂不以人微言轻。故终归于一张休纸也。不无自信之意。故复为誊出前疏而陈之。惟 圣明更加留念焉。(传曰言于备局。备边司 启曰以右副承旨洪镐启辞。 传曰此疏回 启之后。何以不为行会各道乎。问 启事传教矣。当初洪镐上疏。即为覆 启。行会于各道矣。辛巳正月间。庆尚左右兵使因本司行文。束伍军别备私铳之人。开录状 启。限二年一结复户事。亦为定夺行会。其后以郑艗状启观之。右道束伍军之自备。多至二千馀柄。则洪镐居在乡曲。未及闻知官家之事。而有此云云明矣。然至于两湖则无有自备人。驰 启之事。虽或有之。自备者不多。故或未及驰 启之致邪。更为移文问其举行形止何如。 传曰依 启。且本司凡干命令。一番行会而已。其举行与否。不能问知。故每事如此。有司堂上所为殊极非矣。)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祭文
祭愚伏先生文
小子西征。夫子寝疾。小子东还。夫子易箦。吾将安放。吾道之厄。耳谁其提。蒙谁其击。百年馀恸。未承遗嘱。
岁月才周。謦欬已邈。在天星斗。在地山岳。不朽者存。辉映无极。聊奠一酌。伫冀降格。(右再祭文)
哲人在世。瑞世麒麟。哲人弃世。举世荆榛。山颓几日。奄及再期。一声长恸。非但吾私。(右三祭文)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8L 页
 祭李公伯明文
祭李公伯明文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代明。四时之错行。山河之博大。人物之众多。万古之悠久。使之贵使之贱使之祸使之福使之寿使之夭。又使之倏然而生。倏然而死者。未知谁是主张。老兄生于名阀之裔。诗礼之家。而以雍容之资端重之容狷介之操孝友之行。不得有为于当世。且命才过中身而止。信此理之茫茫。曰余无状。童稚之年。始识兄于武夷之里。中心藏而不能忘。辛酉之冬。攀柏于故山。壬戌之岁。奉神舆而入太白也。兄于风雨之夕。以一仆一马。来访问草土中。因横说竖说。出入反覆。又语到时事。悲宇宙之晦塞。愤伦纪之堙没。累累数千言。而言各有当。岂料夫座席之上半饷之间。遽遭鬼物之狞。及其还家。永不见君子之耿光也。言念如玉而难追。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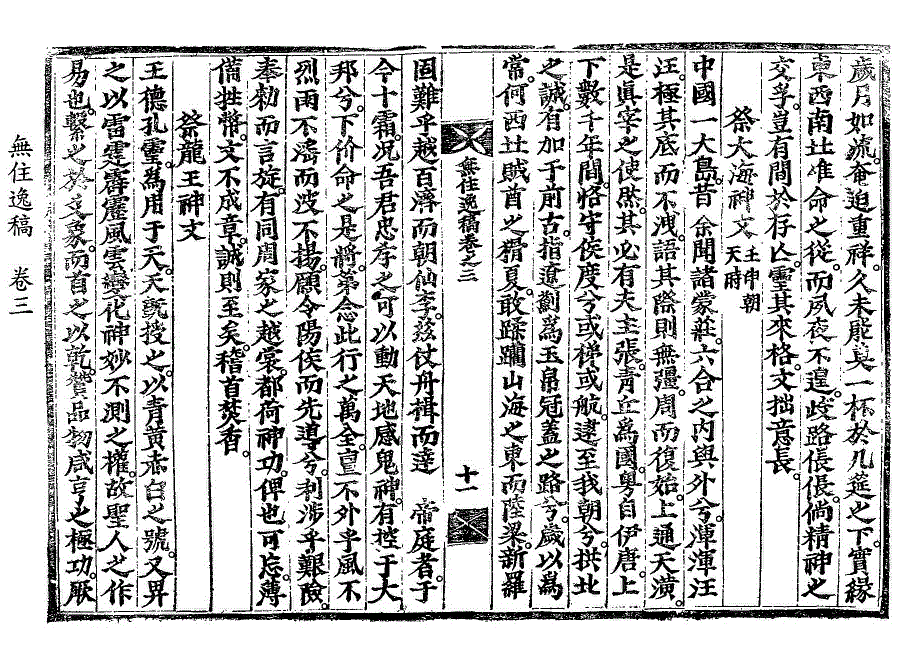 岁月如流。奄迫重祥。久未能莫一杯于几筵之下。实缘东西南北唯命之从。而夙夜不遑。歧路伥伥。倘精神之交孚。岂有间于存亡。灵其来格。文拙意长。
岁月如流。奄迫重祥。久未能莫一杯于几筵之下。实缘东西南北唯命之从。而夙夜不遑。歧路伥伥。倘精神之交孚。岂有间于存亡。灵其来格。文拙意长。祭大海神文(壬申朝天时)
中国一大岛。昔余闻诸蒙庄。六合之内与外兮。浑浑汪汪。极其底而不泄。语其际则无彊。周而复始。上通天潢。是真宰之使然。其必有夫主张。青丘为国。粤自伊唐。上下数千年间。恪守侯度兮或梯或航。逮至我朝兮。拱北之诚。有加于前古。指辽蓟为玉帛冠盖之路兮。岁以为常。何西北贼酋之猾夏。敢蹂躏山海之东而陆梁。新罗固难乎越百济而朝仙李。兹仗舟楫而达 帝庭者。于今十霜。况吾君忠孝之可以动天地感鬼神。有控于大邦兮。下价命之是将。第念此行之万全。亶不外乎风不烈雨不淫而波不扬。愿令阳侯而先导兮。利涉乎艰险。奉敕而言旋。有同周家之越裳。都荷神功。俾也可忘。薄备牲币。文不成章。诚则至矣。稽首焚香。
祭龙王神文
王德孔灵。为用于天。天既授之。以青黄赤白之号。又畀之以雷霆霹雳风云变化神妙不测之权。故圣人之作易也。系之于爻象。而首之以乾。赞品物咸亨之极功。厥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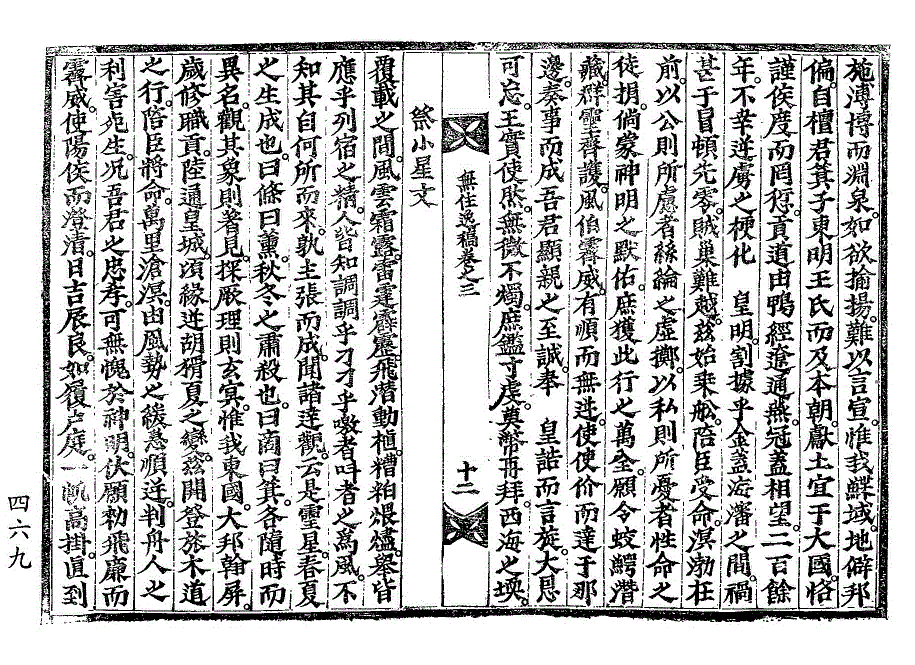 施溥博而渊泉。如欲揄扬。难以言宣。惟我鲽域。地僻邦偏。自檀君箕子东明王氏而及本朝。献土宜于大国。恪谨侯度而罔愆。贡道由鸭经辽通燕。冠盖相望。二百馀年。不幸逆虏之梗化 皇明。割据乎金盖海沈之间。祸甚于冒顿先零。贼巢难越。兹始乘船。陪臣受命。溟渤在前。以公则所虑者丝纶之虚掷。以私则所忧者性命之徒捐。倘蒙神明之默佑。庶获此行之万全。愿令蛟鳄潜藏。群灵齐护。风伯霁威。有顺而无逆。使使价而达于那边。奏事而成吾君显亲之至诚。奉 皇诰而言旋。大恩可忘。王实使然。无微不烛。庶鉴寸虔。莫币再拜。西海之堧。
施溥博而渊泉。如欲揄扬。难以言宣。惟我鲽域。地僻邦偏。自檀君箕子东明王氏而及本朝。献土宜于大国。恪谨侯度而罔愆。贡道由鸭经辽通燕。冠盖相望。二百馀年。不幸逆虏之梗化 皇明。割据乎金盖海沈之间。祸甚于冒顿先零。贼巢难越。兹始乘船。陪臣受命。溟渤在前。以公则所虑者丝纶之虚掷。以私则所忧者性命之徒捐。倘蒙神明之默佑。庶获此行之万全。愿令蛟鳄潜藏。群灵齐护。风伯霁威。有顺而无逆。使使价而达于那边。奏事而成吾君显亲之至诚。奉 皇诰而言旋。大恩可忘。王实使然。无微不烛。庶鉴寸虔。莫币再拜。西海之堧。祭小星文
覆载之间。风云霜露。雷霆霹雳。飞潜动植。糟粕煨烬。举皆应乎列宿之精。人皆知调调乎刁刁乎噭者叫者之为风。不知其自何所而来。孰主张而成。闻诸达观。云是灵星。春夏之生成也。曰条曰薰。秋冬之肃杀也。曰商曰箕。各随时而异名。观其象则著见。探厥理则玄冥。惟我东国。大邦翰屏。岁修职贡。陆通皇城。顷缘逆胡猾夏之变。兹开登旅木道之行。陪臣将命。万里沧溟。由风势之缓急顺逆。判舟人之利害死生。况吾君之忠孝。可无愧于神明。伏愿敕飞廉而霁威。使阳侯而澄清。日吉辰良。如履户庭。一帆高挂。直到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0H 页
 帝京。控子冕旒。竣事旋旌。可忘大德。铭感下情。谓天盖高。上通者诚。无可更陈。仰凭圣灵。
帝京。控子冕旒。竣事旋旌。可忘大德。铭感下情。谓天盖高。上通者诚。无可更陈。仰凭圣灵。祭船神文
冥思物理。神无不在。创自轩皇。于河于海。吾今受命。溟渤之汇。神如勖哉。有辞万载。
再祭文
诸神盛德。已白前文。区区下情。亦既尽言。上帝好生。神必体焉。千万祷祝。利涉遄旋。
三祭文
浩浩茫茫。万里沧溟。靡神畴依。靡神曷行。无作神羞。无落神名。神其在兹。庶鉴寸诚。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杂著
上愚伏先生性理节要问目
论性理。临川吴氏曰云云。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恶浊而污坏其性也。故虽与告子言。而终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读孟子。亦见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信斯言也。是孟子之论性。说得不分明。使告子全然晓不得。其反覆辨论。若有些不快于孟子。而终不归咎于告子之执滞。然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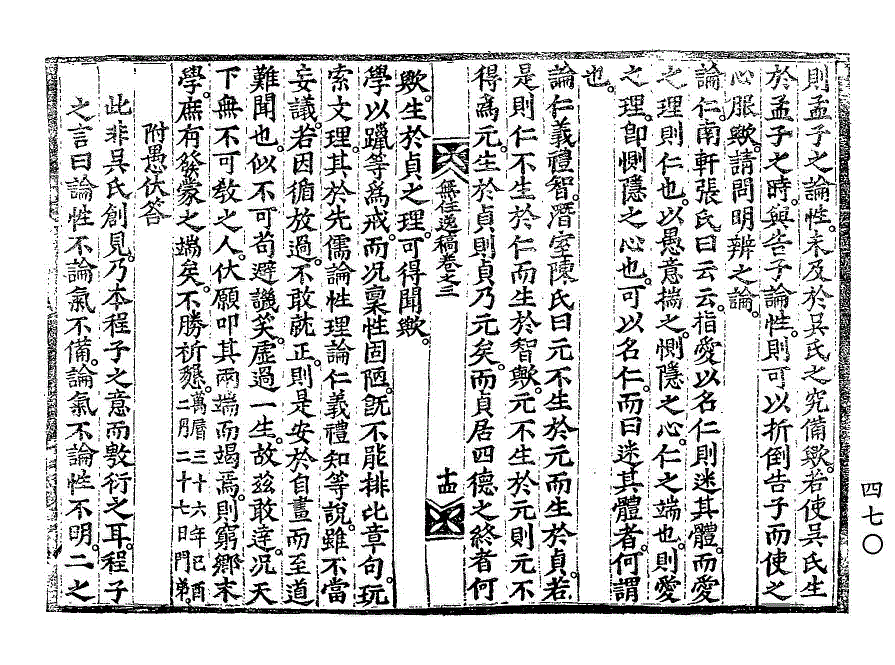 则孟子之论性。未及于吴氏之究备欤。若使吴氏生于孟子之时。与告子论性。则可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欤。请问明辨之论。
则孟子之论性。未及于吴氏之究备欤。若使吴氏生于孟子之时。与告子论性。则可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欤。请问明辨之论。论仁。南轩张氏曰云云。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而爱之理则仁也。以愚意揣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则爱之理。即恻隐之心也。可以名仁。而曰迷其体者。何谓也。
论仁义礼智。潜室陈氏曰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若是则仁不生于仁而生于智欤。元不生于元则元不得为元。生于贞则贞乃元矣。而贞居四德之终者何欤。生于贞之理。可得闻欤。
学以躐等为戒。而况禀性固陋。既不能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其于先儒论性理论仁义礼知等说。虽不当妄议。若因循放过。不敢就正。则是安于自画而至道难闻也。似不可苟避讥笑。虚过一生。故兹敢达。况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伏愿叩其两端而竭焉。则穷乡末学。庶有发蒙之端矣。不胜祈恳。(万历三十六年己酉二月二十七日门弟。)
附愚伏答
此非吴氏创见。乃本程子之意而敷衍之耳。程子之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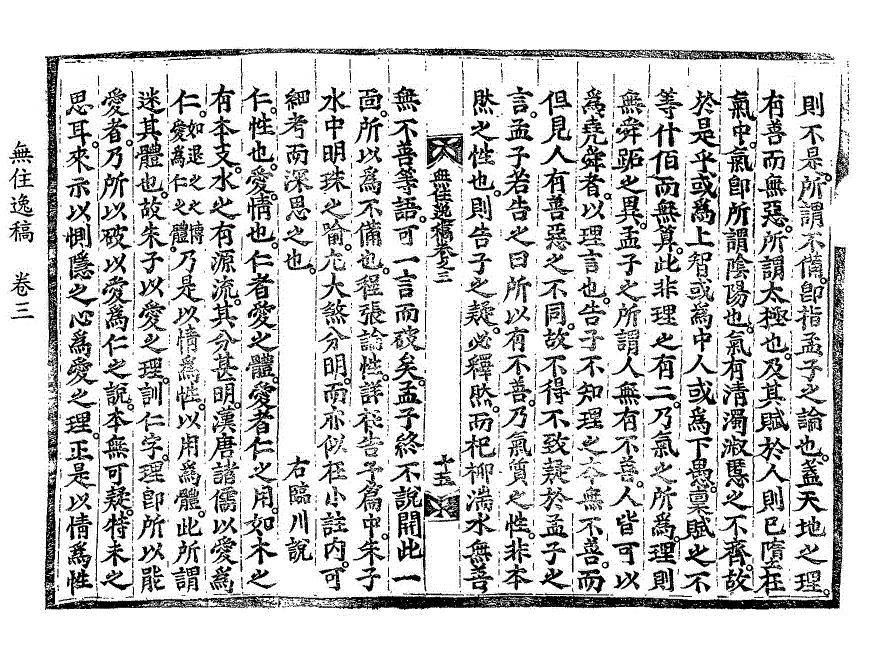 则不是。所谓不备。即指孟子之论也。盖天地之理。有善而无恶。所谓太极也。及其赋于人则已堕在气中。气即所谓阴阳也。气有清浊淑慝之不齐。故于是乎或为上智或为中人或为下愚。禀赋之不等什佰而无算。此非理之有二。乃气之所为。理则无舜蹠之异。孟子之所谓人无有不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理言也。告子不知理之本无不善。而但见人有善恶之不同。故不得不致疑于孟子之言。孟子若告之曰所以有不善。乃气质之性。非本然之性也。则告子之疑。必释然。而杞柳湍水无善无不善等语。可一言而破矣。孟子终不说开此一面。所以为不备也。程张论性。详在告子篇中。朱子水中明珠之喻。尤大煞分明。而亦似在小注内。可细考而深思之也。(右临川说)
则不是。所谓不备。即指孟子之论也。盖天地之理。有善而无恶。所谓太极也。及其赋于人则已堕在气中。气即所谓阴阳也。气有清浊淑慝之不齐。故于是乎或为上智或为中人或为下愚。禀赋之不等什佰而无算。此非理之有二。乃气之所为。理则无舜蹠之异。孟子之所谓人无有不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理言也。告子不知理之本无不善。而但见人有善恶之不同。故不得不致疑于孟子之言。孟子若告之曰所以有不善。乃气质之性。非本然之性也。则告子之疑。必释然。而杞柳湍水无善无不善等语。可一言而破矣。孟子终不说开此一面。所以为不备也。程张论性。详在告子篇中。朱子水中明珠之喻。尤大煞分明。而亦似在小注内。可细考而深思之也。(右临川说)仁。性也。爱。情也。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如木之有本支。水之有源流。其分甚明。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如退之之博爱为仁之体。)乃是以情为性。以用为体。此所谓迷其体也。故朱子以爱之理。训仁字。理即所以能爱者。乃所以破以爱为仁之说。本无可疑。特未之思耳。来示以恻隐之心为爱之理。正是以情为性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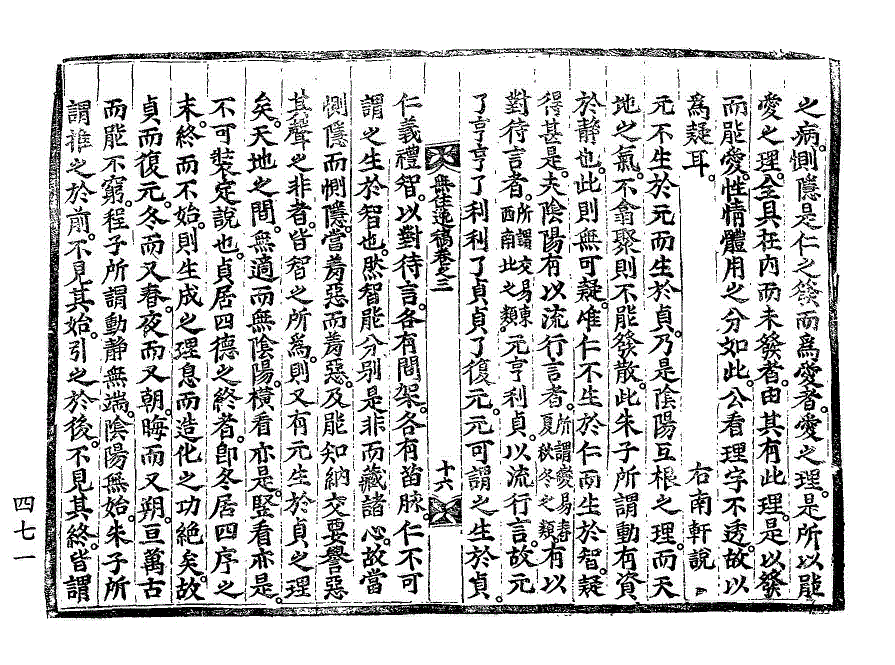 之病。恻隐是仁之发而为爱者。爱之理。是所以能爱之理。全具在内而未发者。由其有此理。是以发而能爱。性情体用之分如此。公看理字不透。故以为疑耳。(右南轩说)
之病。恻隐是仁之发而为爱者。爱之理。是所以能爱之理。全具在内而未发者。由其有此理。是以发而能爱。性情体用之分如此。公看理字不透。故以为疑耳。(右南轩说)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乃是阴阳互根之理。而天地之气。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此朱子所谓动有资于静也。此则无可疑。唯仁不生于仁而生于智。疑得甚是。夫阴阳有以流行言者。(所谓变易春夏秋冬之类。)有以对待言者。(所谓交易东西南北之类。)元亨利贞。以流行言。故元了亨亨了利利了贞贞了复元。元可谓之生于贞。仁义礼智。以对待言。各有间架。各有苗脉。仁不可谓之生于智也。然智能分别是非而藏诸心。故当恻隐而恻隐。当羞恶而羞恶。及能知纳交要誉恶其声之非者。皆智之所为。则又有元生于贞之理矣。天地之间。无适而无阴阳。横看亦是。竖看亦是。不可装定说也。贞居四德之终者。即冬居四序之未。终而不始。则生成之理息而造化之功绝矣。故贞而复元。冬而又春。夜而又朝。晦而又朔。亘万古而能不穷。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朱子所谓推之于前。不见其始。引之于后。不见其终。皆谓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2H 页
 此也。(右潜室说)
此也。(右潜室说)质言(就质于愚伏)
曩者闻曹丈汝益之言。万历纪元庚寅年间。理安士友。鸠材募工。建院于剑岩之下。议以为李阴厓耔,权校理达手可享。进禀于西厓柳先生。则先生谓咸昌又有一奇男子。洪寓庵某是也。不但文章可尚。其节行可为人师表者。而遭时不幸。赍志以殁。其与权李并享。则其建院于士林有光。此则先生微显阐幽之意。而古人所谓伯夷叔齐不遇孔子则只一西山之饿夫者。诚好语也。曹之就正于先生者只此云。而某之闻于曹者。迨将十五年。曹与郑察访汝廓崔丹城时膺诸公。谋复是举。议诸乡友。则或以为当建书院。或以为号乡贤祠。便当建书院云者。李阴厓乃赘于是乡者也。合享之举。甚似苟且。当以权校理洪寓庵享。号乡贤祠便者。以为文匡公于吾乡最先进也。当以文匡为首而次权次洪云。或院或祠之论。纷纭不定。终日喧聒而罢。此则乙卯夏事也。某于其时。适缘遍身针灸。虽不能赴会。而且预料其必有嫌逼事也。厥后闻诸先生平日之论于李仲明季明兄弟。则于永嘉一二建院处。先生乃曰称书院事体重大。当云
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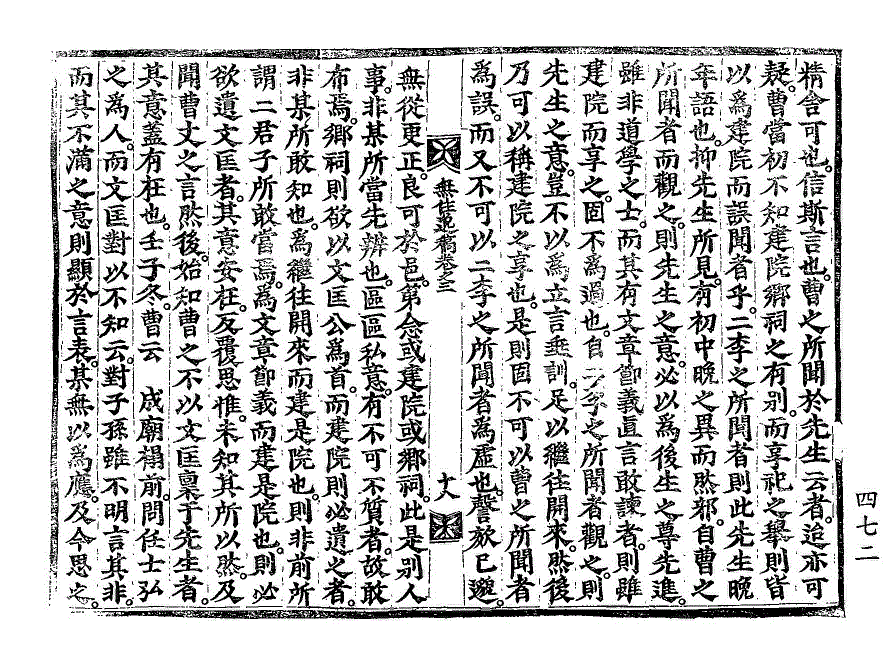 精舍可也。信斯言也。曹之所闻于先生云者。迨亦可疑。曹当初不知建院乡祠之有别。而享祀之举则皆以为建院而误闻者乎。二李之所闻者则此先生晚年语也。抑先生所见。有初中晚之异而然邪。自曹之所闻者而观之。则先生之意。必以为后生之尊先进。虽非道学之士。而其有文章节义直言敢谏者。则虽建院而享之。固不为过也。自二李之所闻者观之。则先生之意。岂不以为立言垂训。足以继往开来。然后乃可以称建院之享也。是则固不可以曹之所闻者为误。而又不可以二李之所闻者为虚也。謦欬已邈。无从更正。良可于邑。第念或建院或乡祠。此是别人事。非某所当先辨也。区区私意。有不可不质者。故敢布焉。乡祠则欲以文匡公为首。而建院则必遗之者。非某所敢知也。为继往开来而建是院也。则非前所谓二君子所敢当焉。为文章节义而建是院也。则必欲遗文匡者。其意安在。反覆思惟。未知其所以然。及闻曹丈之言然后。始知曹之不以文匡禀于先生者。其意盖有在也。壬子冬。曹云 成庙榻前。问任士弘之为人。而文匡对以不知云。对子孙虽不明言其非。而其不满之意则显于言表。某无以为应。及今思之。
精舍可也。信斯言也。曹之所闻于先生云者。迨亦可疑。曹当初不知建院乡祠之有别。而享祀之举则皆以为建院而误闻者乎。二李之所闻者则此先生晚年语也。抑先生所见。有初中晚之异而然邪。自曹之所闻者而观之。则先生之意。必以为后生之尊先进。虽非道学之士。而其有文章节义直言敢谏者。则虽建院而享之。固不为过也。自二李之所闻者观之。则先生之意。岂不以为立言垂训。足以继往开来。然后乃可以称建院之享也。是则固不可以曹之所闻者为误。而又不可以二李之所闻者为虚也。謦欬已邈。无从更正。良可于邑。第念或建院或乡祠。此是别人事。非某所当先辨也。区区私意。有不可不质者。故敢布焉。乡祠则欲以文匡公为首。而建院则必遗之者。非某所敢知也。为继往开来而建是院也。则非前所谓二君子所敢当焉。为文章节义而建是院也。则必欲遗文匡者。其意安在。反覆思惟。未知其所以然。及闻曹丈之言然后。始知曹之不以文匡禀于先生者。其意盖有在也。壬子冬。曹云 成庙榻前。问任士弘之为人。而文匡对以不知云。对子孙虽不明言其非。而其不满之意则显于言表。某无以为应。及今思之。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3H 页
 则某亦有说。小人必挟幼主及昏庸然后。方肆其恶。方 成庙英明。驾驭之日。士弘虽小人。其奸时未暴露。必知者知之而不知者不知耳。及乔桐朝。文匡为守死善道之人。士弘为谄谀逢恶之臣。则谓文匡其无先见之明可矣。若论以知而不言则是依违迁就。费尽心机。全躯保妻子者之所为。未知文匡全其身邪保其妻子邪。身死穷荒。四子连窜。门祸之惨。罔有纪极。而后生辈不但不哀。又欲追咎其不言士弘之奸。其为论不已过乎。且云国史亦书之。此则然矣。史氏之伏柱下记言动例也。君臣答问之语。宁有不书之理。第念当时秉笔之人。此不知文匡之终始者。若及见暮年之事。则其必吐舌否乎。古今天下仁人君子之见卖于小人者何限。寇莱公不知丁谓之奸。胡致堂不知秦桧之邪。司马公不知安石之乱天下。若以是为数君子之病。则文匡之病亦犹是也。文匡又何辞焉。且士君子出处。当观其始终。则 光庙甲戌郎真。文匡于己卯升上舍。辛巳登第。若以金梅月南秋江之洁身物外。窃附于夷齐之流观之。则未知有何所论也。若谓之不仕无义。则文匡非两朝集贤学士者之类。其发身初程。可谓正矣。逮事 成祖。受知
则某亦有说。小人必挟幼主及昏庸然后。方肆其恶。方 成庙英明。驾驭之日。士弘虽小人。其奸时未暴露。必知者知之而不知者不知耳。及乔桐朝。文匡为守死善道之人。士弘为谄谀逢恶之臣。则谓文匡其无先见之明可矣。若论以知而不言则是依违迁就。费尽心机。全躯保妻子者之所为。未知文匡全其身邪保其妻子邪。身死穷荒。四子连窜。门祸之惨。罔有纪极。而后生辈不但不哀。又欲追咎其不言士弘之奸。其为论不已过乎。且云国史亦书之。此则然矣。史氏之伏柱下记言动例也。君臣答问之语。宁有不书之理。第念当时秉笔之人。此不知文匡之终始者。若及见暮年之事。则其必吐舌否乎。古今天下仁人君子之见卖于小人者何限。寇莱公不知丁谓之奸。胡致堂不知秦桧之邪。司马公不知安石之乱天下。若以是为数君子之病。则文匡之病亦犹是也。文匡又何辞焉。且士君子出处。当观其始终。则 光庙甲戌郎真。文匡于己卯升上舍。辛巳登第。若以金梅月南秋江之洁身物外。窃附于夷齐之流观之。则未知有何所论也。若谓之不仕无义。则文匡非两朝集贤学士者之类。其发身初程。可谓正矣。逮事 成祖。受知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3L 页
 最厚。久在。 经幄。补益弘多。而夜对之请。又自文匡始也。此则详在国朝宝鉴。后之人观文匡之久典文柄。皆以文章巨擘知之。而不知当时之论则有不止于文章者。金佔毕之门。语道学则有寒暄一蠹。语隐逸则有南孝温洪裕孙。语文章节义之士则有金濯缨曹梅溪。而佔毕之殁也。其神道铭则出于文匡之手。濯缨又求其父执义公碣铭及思庵等记。寒暄一蠹卓乎其不可尚已。其馀数君子者。皆眼高一世。于人少许可。而必于文匡求之。其所取者不止于文章可知已。事乔桐主也。论打围疏则与议政诸宰。连名上者。而其救李宗准救解儒生论从谏则皆其独劄也。上不负 成祖。下不负所学。则国无道至死不变。庶几近之。而后生辈不能详究其实。直欲以寇胡司马之病。尽没其平生出处之大节。则是洗垢而索瘢也。其所论公乎否邪。权校理直言不讳。身戮阙庭。至今闻之者。赍咨涕洟之不已。洪寓庵早事文章。与郑纯夫,朴仲说诸公相友善。其谪也撰自挽以示乐天知命之意。及其反正也。杜门家居。托以终丧。而其微意则有不足当时之举措者焉。二君子之可祭于社。固无疑也。若推原始终而论之。则际会明时。左右辅
最厚。久在。 经幄。补益弘多。而夜对之请。又自文匡始也。此则详在国朝宝鉴。后之人观文匡之久典文柄。皆以文章巨擘知之。而不知当时之论则有不止于文章者。金佔毕之门。语道学则有寒暄一蠹。语隐逸则有南孝温洪裕孙。语文章节义之士则有金濯缨曹梅溪。而佔毕之殁也。其神道铭则出于文匡之手。濯缨又求其父执义公碣铭及思庵等记。寒暄一蠹卓乎其不可尚已。其馀数君子者。皆眼高一世。于人少许可。而必于文匡求之。其所取者不止于文章可知已。事乔桐主也。论打围疏则与议政诸宰。连名上者。而其救李宗准救解儒生论从谏则皆其独劄也。上不负 成祖。下不负所学。则国无道至死不变。庶几近之。而后生辈不能详究其实。直欲以寇胡司马之病。尽没其平生出处之大节。则是洗垢而索瘢也。其所论公乎否邪。权校理直言不讳。身戮阙庭。至今闻之者。赍咨涕洟之不已。洪寓庵早事文章。与郑纯夫,朴仲说诸公相友善。其谪也撰自挽以示乐天知命之意。及其反正也。杜门家居。托以终丧。而其微意则有不足当时之举措者焉。二君子之可祭于社。固无疑也。若推原始终而论之。则际会明时。左右辅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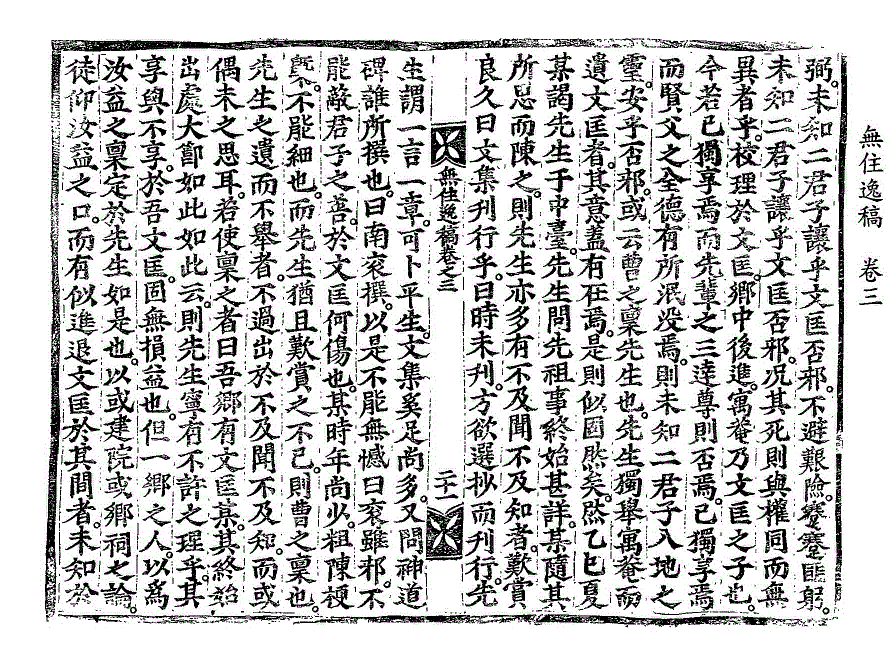 弼。未知二君子让乎文匡否邪。不避艰险。蹇蹇匪躬。未知二君子让乎文匡否邪。况其死则与权同而无异者乎。校理于文匡。乡中后进。寓庵乃文匡之子也。今若己独享焉而先辈之三达尊则否焉。己独享焉而贤父之全德有所泯没焉。则未知二君子入地之灵。安乎否邪。或云曹之禀先生也。先生独举寓庵而遗文匡者。其意盖有在焉。是则似固然矣。然乙巳夏某谒先生于中台。先生问先祖事终始甚详。某随其所思而陈之。则先生亦多有不及闻不及知者。叹赏良久曰文集刊行乎。曰时未刊。方欲选抄而刊行。先生谓一言一章。可卜平生。文集奚足尚多。又问神道碑谁所撰也。曰南衮撰。以是不能无憾曰衮虽邪。不能蔽君子之善。于文匡何伤也。某时年尚少。粗陈梗槩。不能细也。而先生犹且叹赏之不已。则曹之禀也。先生之遗而不举者。不过出于不及闻不及知。而或偶未之思耳。若使禀之者曰吾乡有文匡某。其终始出处大节如此如此云。则先生宁有不许之理乎。其享与不享。于吾文匡。固无损益也。但一乡之人。以为汝益之禀定于先生如是也。以或建院或乡祠之论。徒仰汝益之口。而有似进退文匡于其间者。未知于
弼。未知二君子让乎文匡否邪。不避艰险。蹇蹇匪躬。未知二君子让乎文匡否邪。况其死则与权同而无异者乎。校理于文匡。乡中后进。寓庵乃文匡之子也。今若己独享焉而先辈之三达尊则否焉。己独享焉而贤父之全德有所泯没焉。则未知二君子入地之灵。安乎否邪。或云曹之禀先生也。先生独举寓庵而遗文匡者。其意盖有在焉。是则似固然矣。然乙巳夏某谒先生于中台。先生问先祖事终始甚详。某随其所思而陈之。则先生亦多有不及闻不及知者。叹赏良久曰文集刊行乎。曰时未刊。方欲选抄而刊行。先生谓一言一章。可卜平生。文集奚足尚多。又问神道碑谁所撰也。曰南衮撰。以是不能无憾曰衮虽邪。不能蔽君子之善。于文匡何伤也。某时年尚少。粗陈梗槩。不能细也。而先生犹且叹赏之不已。则曹之禀也。先生之遗而不举者。不过出于不及闻不及知。而或偶未之思耳。若使禀之者曰吾乡有文匡某。其终始出处大节如此如此云。则先生宁有不许之理乎。其享与不享。于吾文匡。固无损益也。但一乡之人。以为汝益之禀定于先生如是也。以或建院或乡祠之论。徒仰汝益之口。而有似进退文匡于其间者。未知于无住先生逸稿卷之三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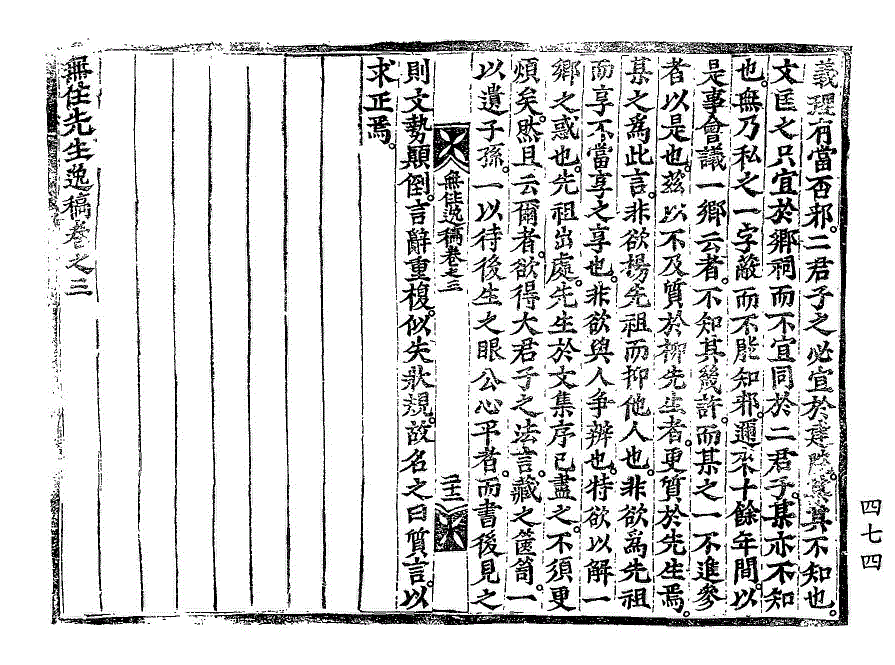 义理有当否邪。二君子之必宜于建院。某其不知也。文匡之只宜于乡祠而不宜同于二君子。某亦不知也。无乃私之一字蔽而不能知邪。迩来十馀年间。以是事会议一乡云者。不知其几许。而某之一不进参者以是也。兹以不及质于柳先生者。更质于先生焉。某之为此言。非欲扬先祖而抑他人也。非欲为先祖而享不当享之享也。非欲与人争辨也。特欲以解一乡之惑也。先祖出处。先生于文集序已尽之。不须更烦矣。然且云尔者。欲得大君子之法言。藏之箧笥。一以遗子孙。一以待后生之眼公心平者。而书后见之则文势颠倒。言辞重复。似失状规。故名之曰质言。以求正焉。
义理有当否邪。二君子之必宜于建院。某其不知也。文匡之只宜于乡祠而不宜同于二君子。某亦不知也。无乃私之一字蔽而不能知邪。迩来十馀年间。以是事会议一乡云者。不知其几许。而某之一不进参者以是也。兹以不及质于柳先生者。更质于先生焉。某之为此言。非欲扬先祖而抑他人也。非欲为先祖而享不当享之享也。非欲与人争辨也。特欲以解一乡之惑也。先祖出处。先生于文集序已尽之。不须更烦矣。然且云尔者。欲得大君子之法言。藏之箧笥。一以遗子孙。一以待后生之眼公心平者。而书后见之则文势颠倒。言辞重复。似失状规。故名之曰质言。以求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