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x 页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疏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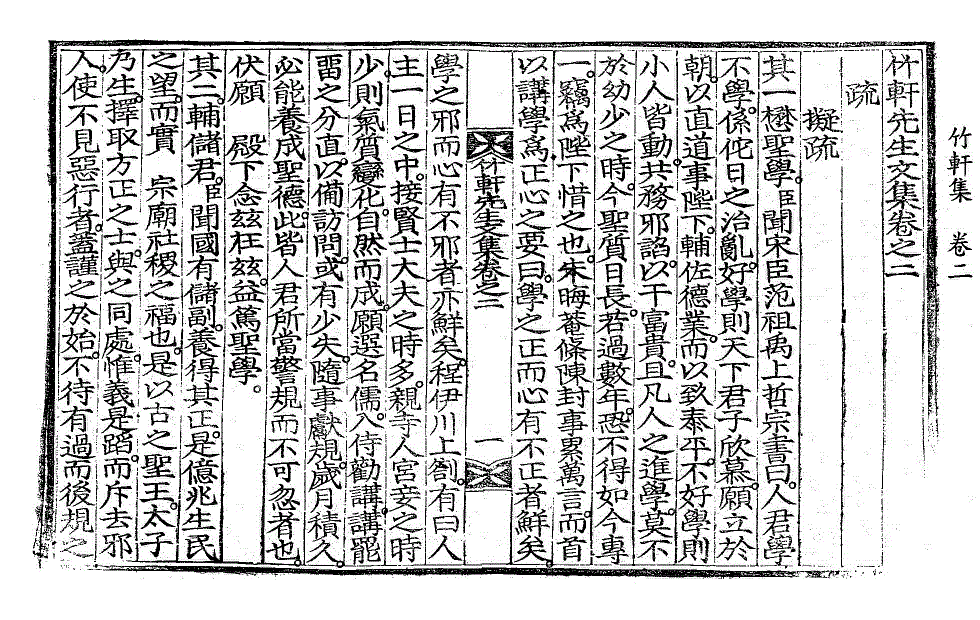 拟疏
拟疏[懋圣学]
其一懋圣学。臣闻宋臣范祖禹上哲宗书曰。人君学不学。系佗日之治乱。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以致泰平。不好学则小人皆动。共务邪谄。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幼少之时。今圣质日长。若过数年。恐不得如今专一。窃为陛下惜之也。朱晦庵条陈封事累万言。而首以讲学为正心之要曰。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程伊川上劄。有曰人主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妾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少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此皆人君所当警规而不可忽者也。伏愿 殿下念玆在玆。益笃圣学。
[辅储君]
其二。辅储君。臣闻国有储副。养得其正。是亿兆生民之望。而实 宗庙社稷之福也。是以古之圣王。太子乃生。择取方正之士。与之同处。惟义是蹈。而斥去邪人。使不见恶行者。盖谨之于始。不待有过而后规之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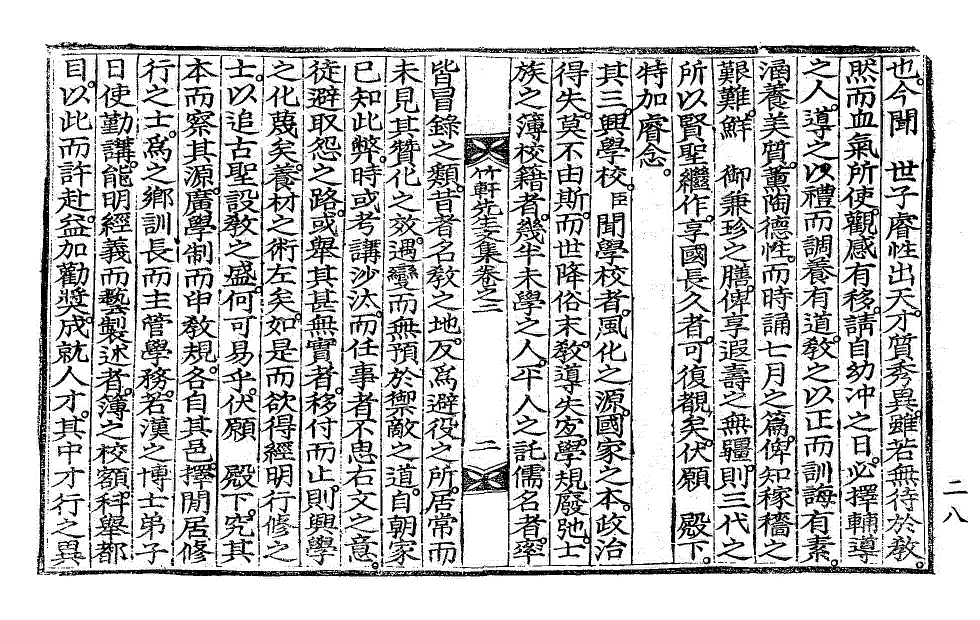 也。今闻 世子睿性出天。才质秀异。虽若无待于教。然而血气所使。观感有移。请自幼冲之日。必择辅导之人。导之以礼而调养有道。教之以正而训诲有素。涵养美质。薰陶德性。而时诵七月之篇。俾知稼穑之艰难。鲜 御兼珍之膳。俾享遐寿之无疆。则三代之所以贤圣继作。享国长久者。可复睹矣。伏愿 殿下。特加睿念。
也。今闻 世子睿性出天。才质秀异。虽若无待于教。然而血气所使。观感有移。请自幼冲之日。必择辅导之人。导之以礼而调养有道。教之以正而训诲有素。涵养美质。薰陶德性。而时诵七月之篇。俾知稼穑之艰难。鲜 御兼珍之膳。俾享遐寿之无疆。则三代之所以贤圣继作。享国长久者。可复睹矣。伏愿 殿下。特加睿念。[兴学校]
其三。兴学校。臣闻学校者。风化之源。国家之本。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而世降俗末。教导失宜。学规废弛。士族之簿校籍者。几半未学之人。平人之托儒名者。率皆冒录之类。昔者名教之地。反为避役之所。居常而未见其赞化之效。遇变而无预于御敌之道。自朝家已知此弊。时或考讲沙汰。而任事者不思右文之意。徒避取怨之路。或举其甚无实者。移付而止。则兴学之化蔑矣。养材之术左矣。如是而欲得经明行修之士。以追古圣设教之盛。何可易乎。伏愿 殿下。究其本而察其源。广学制而申教规。各自其邑。择閒居修行之士。为之乡训长而主管学务。若汉之博士弟子日使勤讲。能明经义而艺制述者。簿之校额。科举都目。以此而许赴。益加劝奖。成就人才。其中才行之异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29H 页
 等者。补试于太学。以资国家之用。而且分遣学官。考训师养成之勤慢。择补参下之职。以为兴起之地。而取其中才鲁学蔑者。移簿于养武所。勿使徵布。择其乡之文武备具者及出身之有识者。名以为教养将。课武艺而教兵书。一如学舍之养士。导之以礼。教之以义。都城内外。亦皆如是。而武科都目。亦以此许赴。且较其师之能否。施赏而劝奖。又择其才艺之特异者。试才于国武所。许以直赴。馀皆作队。而俾无閒游。居常而殖学。遇变而卫国。则国家菁莪之化。文武并用之道。无逾于此矣。
等者。补试于太学。以资国家之用。而且分遣学官。考训师养成之勤慢。择补参下之职。以为兴起之地。而取其中才鲁学蔑者。移簿于养武所。勿使徵布。择其乡之文武备具者及出身之有识者。名以为教养将。课武艺而教兵书。一如学舍之养士。导之以礼。教之以义。都城内外。亦皆如是。而武科都目。亦以此许赴。且较其师之能否。施赏而劝奖。又择其才艺之特异者。试才于国武所。许以直赴。馀皆作队。而俾无閒游。居常而殖学。遇变而卫国。则国家菁莪之化。文武并用之道。无逾于此矣。[用人才]
其四。用人才。臣闻治国之道。在于用人才。而用人之本。在于得贤相。故以尧,舜,汤,文之圣。得稷,离,伊,吕之佐。而野无遗贤之叹。降及后世。少号治平之君。则必师厚德而询咨。且得贤相而倚任。故为其师相者。非但能竭其才而已。又取一时之人才。以成协恭之美。而以今日言之。则虽有管乐之才。三公欲荐而不自由。人主欲用而不能得者何也。庶事之厅废而郎荐之规作。郎荐作而党论起。党论起而士趋歧。某良士某非良士。皆出于好恶。故无论贤不肖。而同其议者。名之以才。不与其议者。称之以不才。苟出乎彼而入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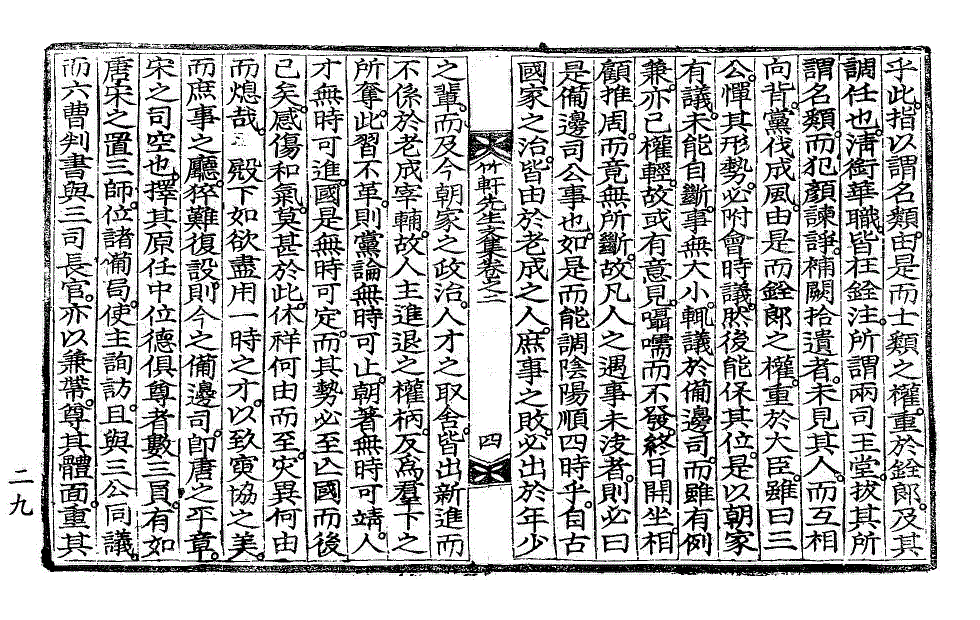 乎此。指以谓名类。由是而士类之权。重于铨郎。及其调任也。清衔华职。皆在铨注。所谓两司玉堂。拔其所谓名类。而犯颜谏诤。补阙拾遗者。未见其人。而互相向背。党伐成风。由是而铨郎之权。重于大臣。虽曰三公。惮其形势。必附会时议。然后能保其位。是以朝家有议。未能自断。事无大小。辄议于备边司。而虽有例兼。亦已权轻。故或有意见。嗫嚅而不发。终日开坐。相顾推周。而竟无所断。故凡人之遇事未决者。则必曰是备边司公事也。如是而能调阴阳顺四时乎。自古国家之治。皆由于老成之人。庶事之败。必出于年少之辈。而及今朝家之政治。人才之取舍。皆出新进而不系于老成宰辅。故人主进退之权柄。反为群下之所夺。此习不革。则党论无时可止。朝著无时可靖。人才无时可进。国是无时可定。而其势必至亡国而后已矣。感伤和气。莫甚于此。休祥何由而至。灾异何由而熄哉。 殿下如欲尽用一时之才。以致寅协之美。而庶事之厅。猝难复设。则今之备边司。即唐之平章。宋之司空也。择其原任中位德俱尊者数三员。有如唐,宋之置三师。位诸备局。使主询访。且与三公同议。而六曹判书与三司长官。亦以兼带。尊其体面。重其
乎此。指以谓名类。由是而士类之权。重于铨郎。及其调任也。清衔华职。皆在铨注。所谓两司玉堂。拔其所谓名类。而犯颜谏诤。补阙拾遗者。未见其人。而互相向背。党伐成风。由是而铨郎之权。重于大臣。虽曰三公。惮其形势。必附会时议。然后能保其位。是以朝家有议。未能自断。事无大小。辄议于备边司。而虽有例兼。亦已权轻。故或有意见。嗫嚅而不发。终日开坐。相顾推周。而竟无所断。故凡人之遇事未决者。则必曰是备边司公事也。如是而能调阴阳顺四时乎。自古国家之治。皆由于老成之人。庶事之败。必出于年少之辈。而及今朝家之政治。人才之取舍。皆出新进而不系于老成宰辅。故人主进退之权柄。反为群下之所夺。此习不革。则党论无时可止。朝著无时可靖。人才无时可进。国是无时可定。而其势必至亡国而后已矣。感伤和气。莫甚于此。休祥何由而至。灾异何由而熄哉。 殿下如欲尽用一时之才。以致寅协之美。而庶事之厅。猝难复设。则今之备边司。即唐之平章。宋之司空也。择其原任中位德俱尊者数三员。有如唐,宋之置三师。位诸备局。使主询访。且与三公同议。而六曹判书与三司长官。亦以兼带。尊其体面。重其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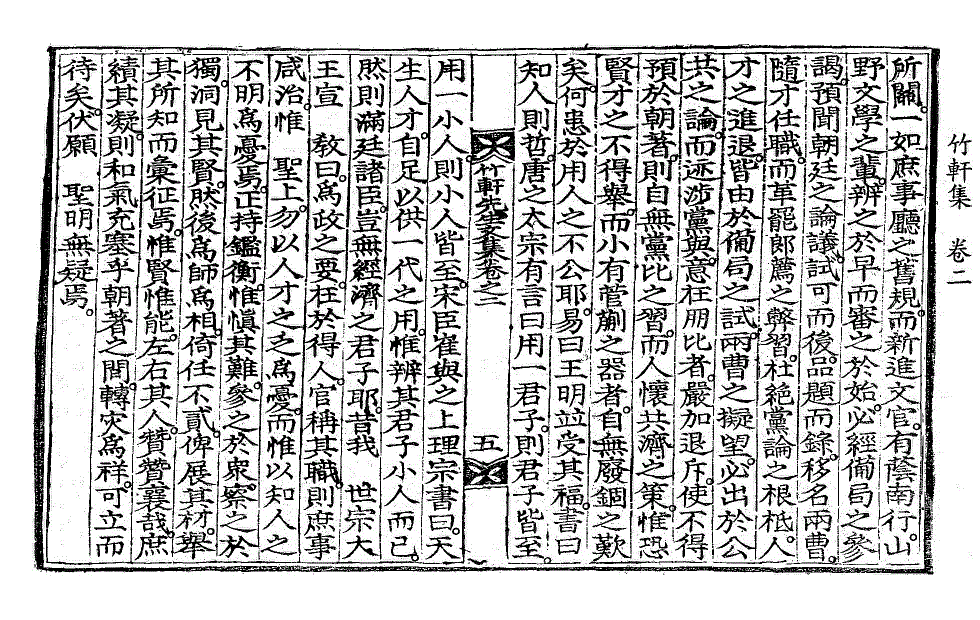 所关。一如庶事厅之旧规。而新进文官。有荫南行。山野文学之辈。辨之于早而审之于始。必经备局之参谒。预闻朝廷之论议。试可而后。品题而录。移名两曹。随才任职。而革罢郎荐之弊习。杜绝党论之根柢。人才之进退。皆由于备局之试。两曹之拟望。必出于公共之论。而迹涉党与。意在朋比者。严加退斥。使不得预于朝著。则自无党比之习。而人怀共济之策。惟恐贤才之不得举。而小有菅蒯之器者。自无废锢之叹矣。何患于用人之不公耶。易曰王明并受其福。书曰知人则哲。唐之太宗有言曰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皆至。宋臣崔与之上理宗书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则满廷诸臣。岂无经济之君子耶。昔我 世宗大王宣 教曰。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官称其职。则庶事咸治。惟 圣上。勿以人才之乏为忧。而惟以知人之不明为忧焉。正持鉴衡。惟慎其难。参之于众。察之于独。洞见其贤。然后为师为相。倚任不贰。俾展其材。举其所知而汇征焉。惟贤惟能。左右其人。赞赞襄哉。庶绩其凝。则和气充塞乎朝著之间。转灾为祥。可立而待矣。伏愿 圣明无疑焉。
所关。一如庶事厅之旧规。而新进文官。有荫南行。山野文学之辈。辨之于早而审之于始。必经备局之参谒。预闻朝廷之论议。试可而后。品题而录。移名两曹。随才任职。而革罢郎荐之弊习。杜绝党论之根柢。人才之进退。皆由于备局之试。两曹之拟望。必出于公共之论。而迹涉党与。意在朋比者。严加退斥。使不得预于朝著。则自无党比之习。而人怀共济之策。惟恐贤才之不得举。而小有菅蒯之器者。自无废锢之叹矣。何患于用人之不公耶。易曰王明并受其福。书曰知人则哲。唐之太宗有言曰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皆至。宋臣崔与之上理宗书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则满廷诸臣。岂无经济之君子耶。昔我 世宗大王宣 教曰。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官称其职。则庶事咸治。惟 圣上。勿以人才之乏为忧。而惟以知人之不明为忧焉。正持鉴衡。惟慎其难。参之于众。察之于独。洞见其贤。然后为师为相。倚任不贰。俾展其材。举其所知而汇征焉。惟贤惟能。左右其人。赞赞襄哉。庶绩其凝。则和气充塞乎朝著之间。转灾为祥。可立而待矣。伏愿 圣明无疑焉。[振纪纲]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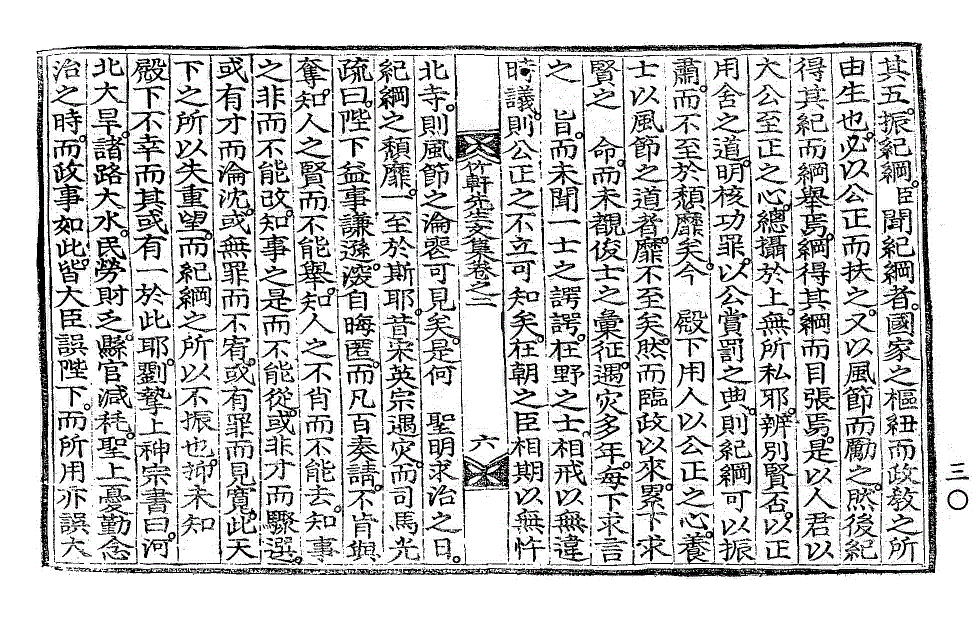 其五。振纪纲。臣闻纪纲者。国家之枢纽而政教之所由生也。必以公正而扶之。又以风节而励之。然后纪得其纪而纲举焉。纲得其纲而目张焉。是以人君以大公至正之心。总摄于上。无所私邪。辨别贤否。以正用舍之道。明核功罪。以公赏罚之典。则纪纲可以振肃。而不至于颓靡矣。今 殿下用人以公正之心。养士以风节之道者。靡不至矣。然而临政以来。累下求贤之 命。而未睹俊士之汇征。遇灾多年。每下求言之 旨。而未闻一士之谔谔。在野之士。相戒以无违时议。则公正之不立可知矣。在朝之臣相期以无忤北寺。则风节之沦丧可见矣。是何 圣明求治之日。纪纲之颓靡。一至于斯耶。昔宋英宗遇灾。而司马光疏曰。陛下益事谦逊。深自晦匿。而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而不能举。知人之不肖而不能去。知事之非而不能改。知事之是而不能从。或非才而骤选。或有才而沦沈。或无罪而不宥。或有罪而见宽。此天下之所以失重望。而纪纲之所以不振也。抑未知 殿下不幸而其或有一于此耶。刘挚上神宗书曰。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劳财乏。县官减秏。圣上忧勤念治之时。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误陛下。而所用亦误大
其五。振纪纲。臣闻纪纲者。国家之枢纽而政教之所由生也。必以公正而扶之。又以风节而励之。然后纪得其纪而纲举焉。纲得其纲而目张焉。是以人君以大公至正之心。总摄于上。无所私邪。辨别贤否。以正用舍之道。明核功罪。以公赏罚之典。则纪纲可以振肃。而不至于颓靡矣。今 殿下用人以公正之心。养士以风节之道者。靡不至矣。然而临政以来。累下求贤之 命。而未睹俊士之汇征。遇灾多年。每下求言之 旨。而未闻一士之谔谔。在野之士。相戒以无违时议。则公正之不立可知矣。在朝之臣相期以无忤北寺。则风节之沦丧可见矣。是何 圣明求治之日。纪纲之颓靡。一至于斯耶。昔宋英宗遇灾。而司马光疏曰。陛下益事谦逊。深自晦匿。而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而不能举。知人之不肖而不能去。知事之非而不能改。知事之是而不能从。或非才而骤选。或有才而沦沈。或无罪而不宥。或有罪而见宽。此天下之所以失重望。而纪纲之所以不振也。抑未知 殿下不幸而其或有一于此耶。刘挚上神宗书曰。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劳财乏。县官减秏。圣上忧勤念治之时。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误陛下。而所用亦误大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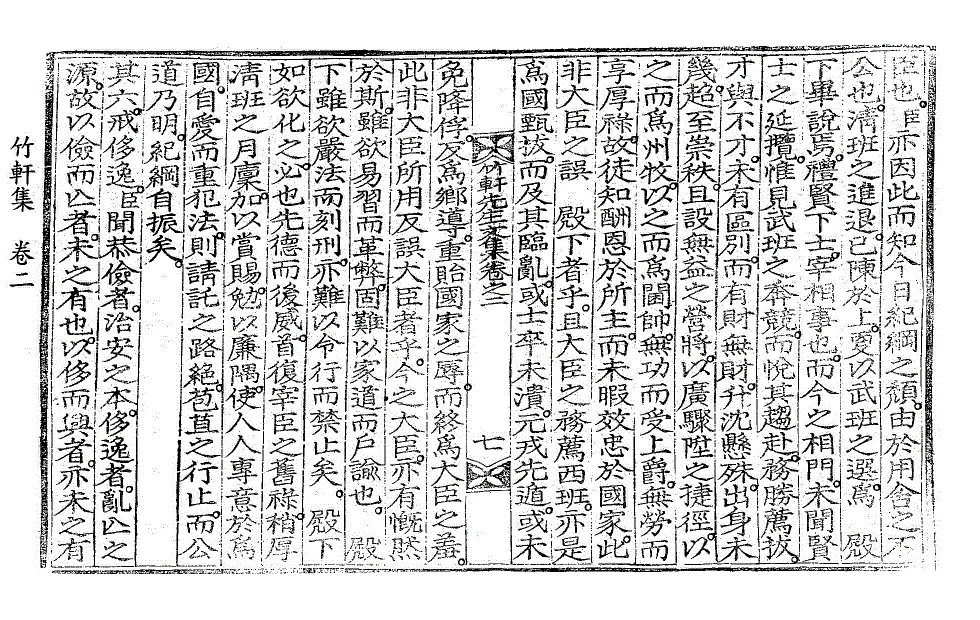 臣也。臣亦因此而知今日纪纲之颓。由于用舍之不公也。清班之进退。已陈于上。更以武班之选。为 殿下毕说焉。礼贤下士。宰相事也。而今之相门。未闻贤士之廷揽。惟见武班之奔竞。而悦其趋赴。务胜荐拔。才与不才。未有区别。而有财无财。升沈悬殊。出身未几。超至崇秩。且设无益之营将。以广骤升之捷径。以之而为州牧。以之而为阃帅。无功而受上爵。无劳而享厚禄。故徒知酬恩于所主。而未暇效忠于国家。此非大臣之误 殿下者乎。且大臣之务荐西班。亦是为国甄拔。而及其临乱。或士卒未溃。元戎先遁。或未免降俘。反为乡导。重贻国家之辱。而终为大臣之羞。此非大臣所用反误大臣者乎。今之大臣。亦有慨然于斯。虽欲易习而革弊。固难以家道而户谕也。 殿下虽欲严法而刻刑。亦难以令行而禁止矣。 殿下如欲化之。必也先德而后威。首复宰臣之旧禄。稍厚清班之月廪。加以赏赐。勉以廉隅。使人人专意于为国。自爱而重犯法。则请托之路绝。苞苴之行止。而公道乃明。纪纲自振矣。
臣也。臣亦因此而知今日纪纲之颓。由于用舍之不公也。清班之进退。已陈于上。更以武班之选。为 殿下毕说焉。礼贤下士。宰相事也。而今之相门。未闻贤士之廷揽。惟见武班之奔竞。而悦其趋赴。务胜荐拔。才与不才。未有区别。而有财无财。升沈悬殊。出身未几。超至崇秩。且设无益之营将。以广骤升之捷径。以之而为州牧。以之而为阃帅。无功而受上爵。无劳而享厚禄。故徒知酬恩于所主。而未暇效忠于国家。此非大臣之误 殿下者乎。且大臣之务荐西班。亦是为国甄拔。而及其临乱。或士卒未溃。元戎先遁。或未免降俘。反为乡导。重贻国家之辱。而终为大臣之羞。此非大臣所用反误大臣者乎。今之大臣。亦有慨然于斯。虽欲易习而革弊。固难以家道而户谕也。 殿下虽欲严法而刻刑。亦难以令行而禁止矣。 殿下如欲化之。必也先德而后威。首复宰臣之旧禄。稍厚清班之月廪。加以赏赐。勉以廉隅。使人人专意于为国。自爱而重犯法。则请托之路绝。苞苴之行止。而公道乃明。纪纲自振矣。[戒侈逸]
其六。戒侈逸。臣闻恭俭者。治安之本。侈逸者。乱亡之源。故以俭而亡者。未之有也。以侈而兴者。亦未之有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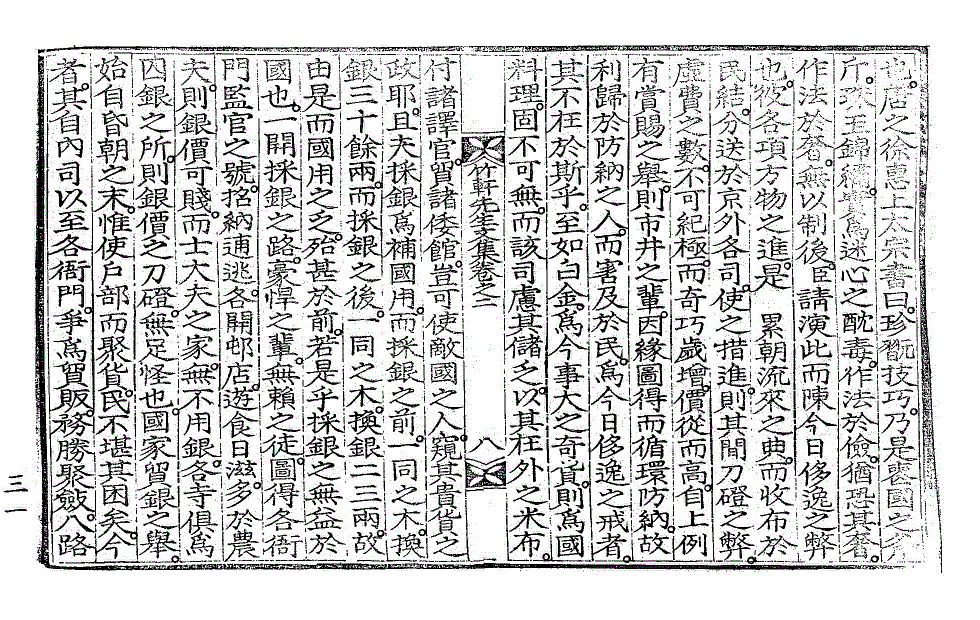 也。唐之徐惠上太宗书曰。珍玩技巧。乃是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为迷心之酖毒。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无以制后。臣请演此而陈今日侈逸之弊也。彼各项方物之进。是 累朝流来之典。而收布于民结。分送于京外各司。使之措进。则其间刀磴之弊。虚费之数。不可纪极。而奇巧岁增。价从而高。自上例有赏赐之举。则市井之辈。因缘图得而循环防纳。故利归于防纳之人。而害及于民。为今日侈逸之戒者。其不在于斯乎。至如白金。为今事大之奇货。则为国料理。固不可无。而该司虑其储乏。以其在外之米布。付诸译官。贸诸倭馆。岂可使敌国之人。窥其贵货之政耶。且夫采银为补国用。而采银之前。一同之木。换银三十馀两。而采银之后。一同之木。换银二三两。故由是而国用之乏。殆甚于前。若是乎采银之无益于国也。一开采银之路。豪悍之辈。无赖之徒。图得各衙门监官之号。招纳逋逃。各开村店。游食日滋。多于农夫。则银价可贱。而士大夫之家。无不用银。各寺俱为囚银之所。则银价之刀磴。无足怪也。国家贸银之举。始自昏朝之末。惟使户部而聚货。民不堪其困矣。今者。其自内司以至各衙门。争为贸贩。务胜聚敛。八路
也。唐之徐惠上太宗书曰。珍玩技巧。乃是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为迷心之酖毒。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无以制后。臣请演此而陈今日侈逸之弊也。彼各项方物之进。是 累朝流来之典。而收布于民结。分送于京外各司。使之措进。则其间刀磴之弊。虚费之数。不可纪极。而奇巧岁增。价从而高。自上例有赏赐之举。则市井之辈。因缘图得而循环防纳。故利归于防纳之人。而害及于民。为今日侈逸之戒者。其不在于斯乎。至如白金。为今事大之奇货。则为国料理。固不可无。而该司虑其储乏。以其在外之米布。付诸译官。贸诸倭馆。岂可使敌国之人。窥其贵货之政耶。且夫采银为补国用。而采银之前。一同之木。换银三十馀两。而采银之后。一同之木。换银二三两。故由是而国用之乏。殆甚于前。若是乎采银之无益于国也。一开采银之路。豪悍之辈。无赖之徒。图得各衙门监官之号。招纳逋逃。各开村店。游食日滋。多于农夫。则银价可贱。而士大夫之家。无不用银。各寺俱为囚银之所。则银价之刀磴。无足怪也。国家贸银之举。始自昏朝之末。惟使户部而聚货。民不堪其困矣。今者。其自内司以至各衙门。争为贸贩。务胜聚敛。八路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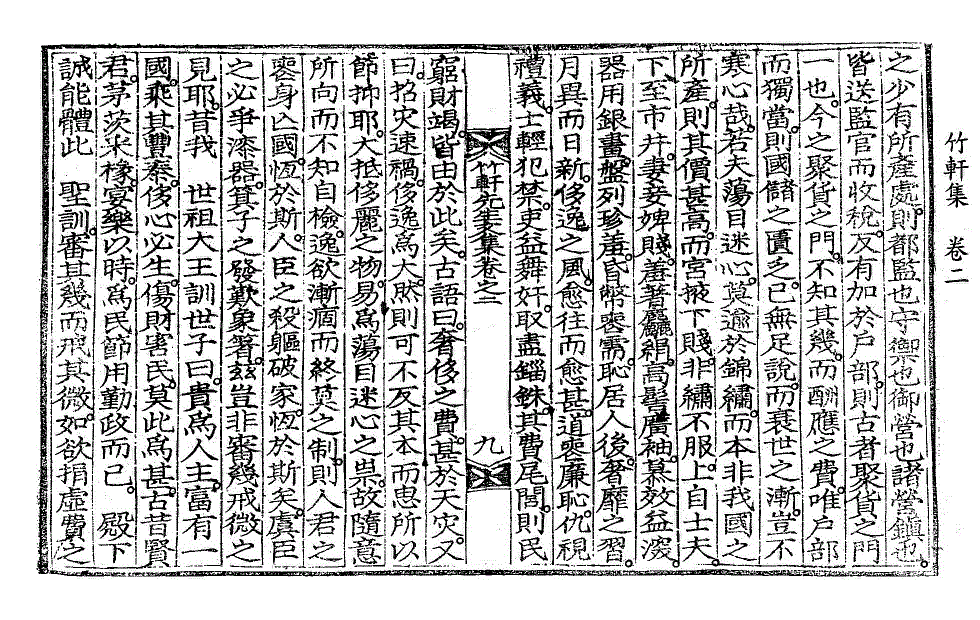 之少有所产处。则都监也守御也御营也诸营镇也。皆送监官而收税。反有加于户部。则古者聚货之门一也。今之聚货之门。不知其几。而酬应之费。唯户部而独当。则国储之匮乏。已无足说。而衰世之渐。岂不寒心哉。若夫荡目迷心。莫逾于锦绣。而本非我国之所产。则其价甚高。而宫掖下贱。非绣不服。上自士夫。下至市井。妻妾婢贱。羞著粗绢。高髻广袖。慕效益深。器用银画。盘列珍羞。昏币丧需。耻居人后。奢靡之习。月异而日新。侈逸之风。愈往而愈甚。道丧廉耻。仇视礼义。士轻犯禁。吏益舞奸。取尽锱铢。其费尾闾。则民穷财竭。皆由于此矣。古语曰。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曰。招灾速祸。侈逸为大。然则可不反其本而思所以节抑耶。大抵侈丽之物。易为荡目迷心之祟。故随意所向而不知自检。逸欲渐痼而终莫之制。则人君之丧身亡国。恒于斯。人臣之杀躯破家。恒于斯矣。虞臣之必争漆器。箕子之发叹象箸。玆岂非审几戒微之见耶。昔我 世祖大王训世子曰。贵为人主。富有一国。乘其丰泰。侈心必生。伤财害民。莫此为甚。古昔贤君。茅茨采椽。宴乐以时。为民节用勤政而已。 殿下诚能体此 圣训。审其几而戒其微。如欲捐虚费之
之少有所产处。则都监也守御也御营也诸营镇也。皆送监官而收税。反有加于户部。则古者聚货之门一也。今之聚货之门。不知其几。而酬应之费。唯户部而独当。则国储之匮乏。已无足说。而衰世之渐。岂不寒心哉。若夫荡目迷心。莫逾于锦绣。而本非我国之所产。则其价甚高。而宫掖下贱。非绣不服。上自士夫。下至市井。妻妾婢贱。羞著粗绢。高髻广袖。慕效益深。器用银画。盘列珍羞。昏币丧需。耻居人后。奢靡之习。月异而日新。侈逸之风。愈往而愈甚。道丧廉耻。仇视礼义。士轻犯禁。吏益舞奸。取尽锱铢。其费尾闾。则民穷财竭。皆由于此矣。古语曰。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曰。招灾速祸。侈逸为大。然则可不反其本而思所以节抑耶。大抵侈丽之物。易为荡目迷心之祟。故随意所向而不知自检。逸欲渐痼而终莫之制。则人君之丧身亡国。恒于斯。人臣之杀躯破家。恒于斯矣。虞臣之必争漆器。箕子之发叹象箸。玆岂非审几戒微之见耶。昔我 世祖大王训世子曰。贵为人主。富有一国。乘其丰泰。侈心必生。伤财害民。莫此为甚。古昔贤君。茅茨采椽。宴乐以时。为民节用勤政而已。 殿下诚能体此 圣训。审其几而戒其微。如欲捐虚费之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2L 页
 资。作福利之基。则进献方物。固难革罢。而择其技巧而有害于俭德者。裁减之。进御诸具。惟取朴素。若其完固而不污者。待其弊而改捧。其于赏赐。必待有功。而且令该曹称物定价。则供亿之费可减。而穷困之民。庶有苏息之望矣。该司贸银。虽云不已之举。而殊非盛世之事。上启利货。下效尤甚。世道日卑。俗尚渐污。金之多也。指为名家。故营镇各邑。贸银成风。牟利横敛之状。无异于癸亥之前。贪饕爻象。必非祥兆。此宜 圣明深加睿念处也。傥能崇俭而斥奢。去侈而贱货。先破内藏。以示王者之无私。椒庭之金。内帑之银。各司之货。移藏于户部。则酬应之外。总是国用矣。躬行以清俭之德。励下以廉介之风。使士夫而耻藏银货。则在朝诸臣。莫不洗心易虑。仰体 圣意。而视金银如土。其价自然贱矣。此后诸处酬应之际。银或不足。以米绵贸用于市上。亦必裕馀矣。伏愿 殿下。思唐宗藏珠之语。念宋祖守财之戒。法天地之节。省用度之烦。内全廉净之德。外绝戕贼之累。崇俭以厚俗。约己以泽物。先垂衣弋绨之化。次明表贵贱之章。则法不须严密。令不待苛㬥。而缙绅耻为奢靡之习。士民争为朴素之风。恶食卑服之治。捐金弃珠之化。
资。作福利之基。则进献方物。固难革罢。而择其技巧而有害于俭德者。裁减之。进御诸具。惟取朴素。若其完固而不污者。待其弊而改捧。其于赏赐。必待有功。而且令该曹称物定价。则供亿之费可减。而穷困之民。庶有苏息之望矣。该司贸银。虽云不已之举。而殊非盛世之事。上启利货。下效尤甚。世道日卑。俗尚渐污。金之多也。指为名家。故营镇各邑。贸银成风。牟利横敛之状。无异于癸亥之前。贪饕爻象。必非祥兆。此宜 圣明深加睿念处也。傥能崇俭而斥奢。去侈而贱货。先破内藏。以示王者之无私。椒庭之金。内帑之银。各司之货。移藏于户部。则酬应之外。总是国用矣。躬行以清俭之德。励下以廉介之风。使士夫而耻藏银货。则在朝诸臣。莫不洗心易虑。仰体 圣意。而视金银如土。其价自然贱矣。此后诸处酬应之际。银或不足。以米绵贸用于市上。亦必裕馀矣。伏愿 殿下。思唐宗藏珠之语。念宋祖守财之戒。法天地之节。省用度之烦。内全廉净之德。外绝戕贼之累。崇俭以厚俗。约己以泽物。先垂衣弋绨之化。次明表贵贱之章。则法不须严密。令不待苛㬥。而缙绅耻为奢靡之习。士民争为朴素之风。恶食卑服之治。捐金弃珠之化。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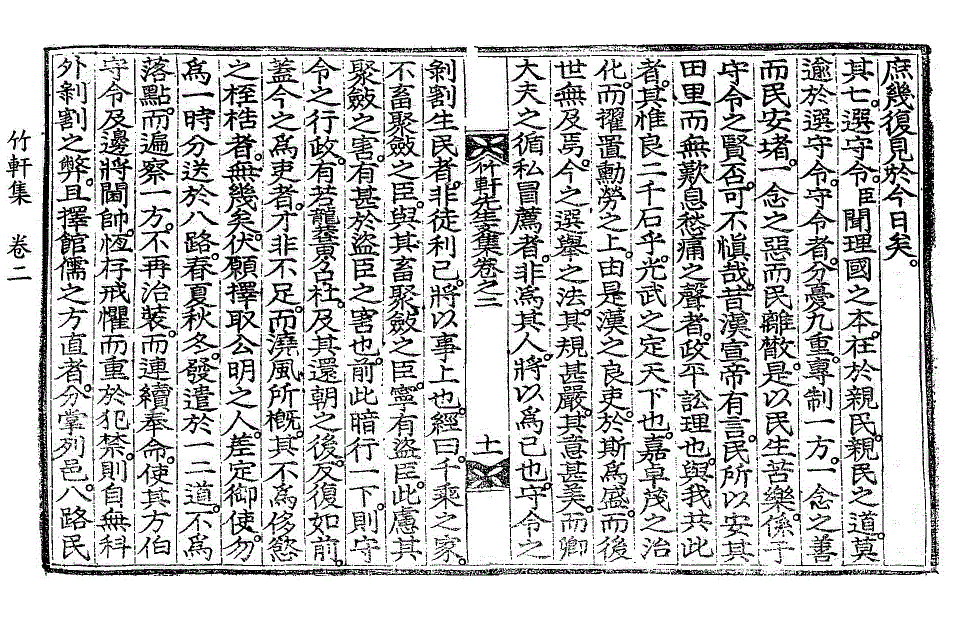 庶几复见于今日矣。
庶几复见于今日矣。[选守令]
其七。选守令。臣闻理国之本。在于亲民。亲民之道。莫逾于选守令。守令者。分忧九重。专制一方。一念之善而民安堵。一念之恶而民离散。是以民生苦乐。系于守令之贤否。可不慎哉。昔汉宣帝有言。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痛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之定天下也。嘉卓茂之治化。而擢置勋劳之上。由是汉之良吏。于斯为盛。而后世无及焉。今之选举之法。其规甚严。其意甚美。而卿大夫之循私冒荐者。非为其人。将以为己也。守令之剥割生民者。非徒利己。将以事上也。经曰。千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畜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虑其聚敛之害。有甚于盗臣之害也。前此暗行一下。则守令之行政。有若龚,黄,召,杜。及其还朝之后。反复如前。盖今之为吏者。才非不足。而浇风所概。其不为侈欲之桎梏者。无几矣。伏愿择取公明之人。差定御使。勿为一时分送于八路。春夏秋冬。发遣于一二道。不为落点。而遍察一方。不再治装。而连续奉命。使其方伯守令及边将阃帅。恒存戒惧而重于犯禁。则自无科外剥割之弊。且择馆儒之方直者。分掌列邑。八路民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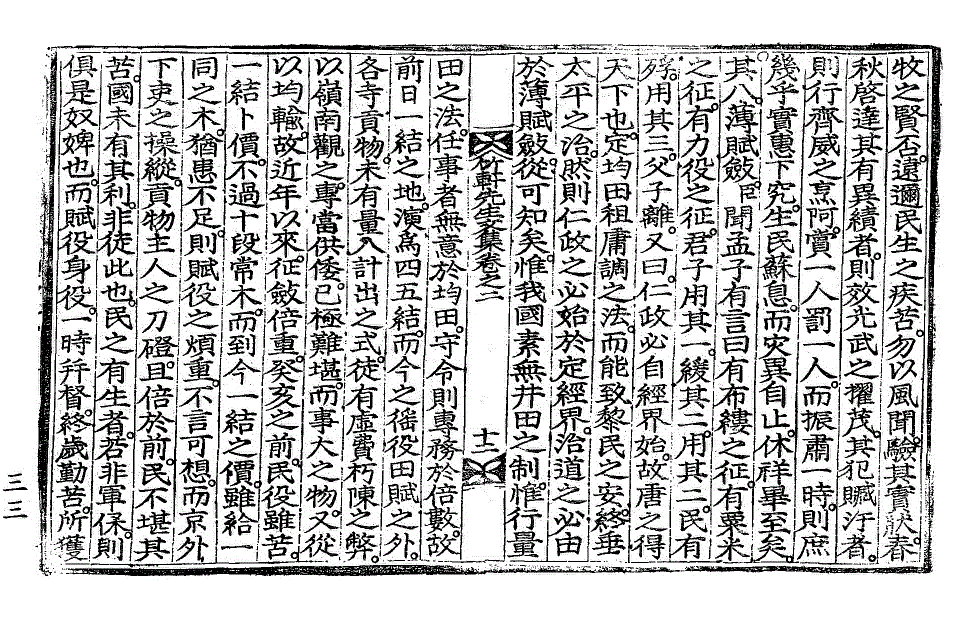 牧之贤否。远迩民生之疾苦。勿以风闻。验其实状。春秋启达其有异绩者。则效光武之擢茂。其犯赃污者。则行齐威之烹阿。赏一人罚一人。而振肃一时。则庶几乎实惠下究。生民苏息。而灾异自止。休祥毕至矣。
牧之贤否。远迩民生之疾苦。勿以风闻。验其实状。春秋启达其有异绩者。则效光武之擢茂。其犯赃污者。则行齐威之烹阿。赏一人罚一人。而振肃一时。则庶几乎实惠下究。生民苏息。而灾异自止。休祥毕至矣。[薄赋敛]
其八。薄赋敛。臣闻孟子有言曰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民有殍。用其三。父子离。又曰。仁政必自经界始。故唐之得天下也。定均田租庸调之法。而能致黎民之安。终垂太平之治。然则仁政之必始于定经界。治道之必由于薄赋敛。从可知矣。惟我国素无井田之制。惟行量田之法。任事者无意于均田。守令则专务于倍数。故前日一结之地。演为四五结。而今之徭役田赋之外。各寺贡物。未有量入计出之式。徒有虚费朽陈之弊。以岭南观之。专当供倭。已极难堪。而事大之物。又从以均输。故近年以来。征敛倍重。癸亥之前。民役虽苦。一结卜价。不过十段常木。而到今一结之价。虽给一同之木。犹患不足。则赋役之烦重。不言可想。而京外下吏之操纵。贡物主人之刀磴。且倍于前。民不堪其苦。国未有其利。非徒此也。民之有生者。若非军保。则俱是奴婢也。而赋役身役。一时并督。终岁勤苦。所获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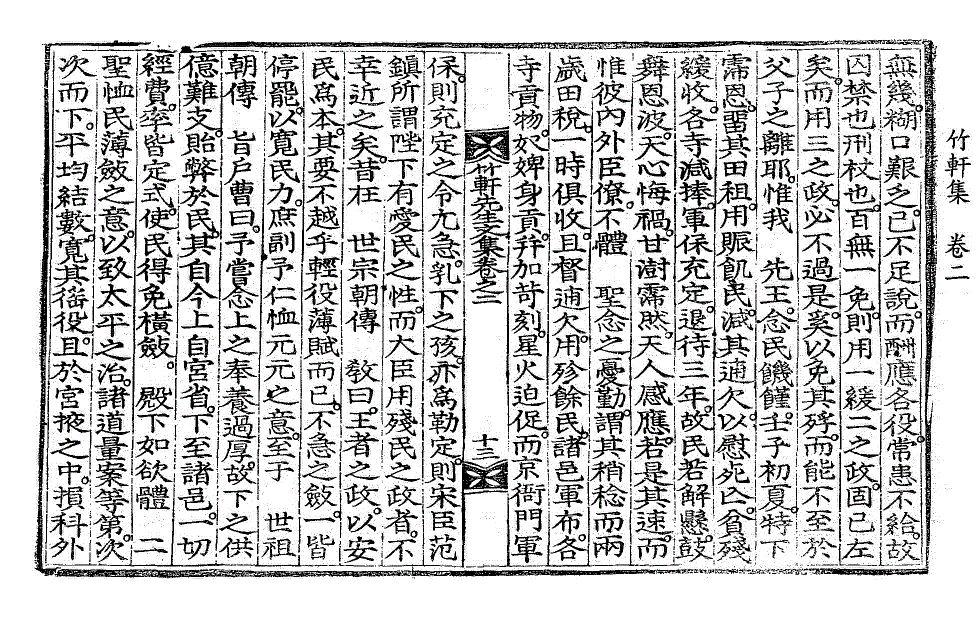 无几。糊口艰乏。已不足说。而酬应各役。常患不给。故囚禁也刑杖也。百无一免。则用一缓二之政。固已左矣。而用三之政。必不过是。奚以免其殍。而能不至于父子之离耶。惟我 先王。念民饥馑。壬子初夏。特下霈恩。留其田租。用赈饥民。减其逋欠。以慰死亡。贫残缓收。各寺减捧。军保充定。退待三年。故民若解悬。鼓舞恩波。天心悔祸。甘澍霈然。天人感应。若是其速。而惟彼内外臣僚。不体 圣念之忧勤。谓其稍稔而两岁田税。一时俱收。且督逋欠。用殄馀民。诸邑军布。各寺贡物。奴婢身贡。并加苛刻。星火迫促。而京衙门军保。则充定之令尤急。乳下之孩。亦为勒定。则宋臣范镇所谓陛下有爱民之性。而大臣用残民之政者。不幸近之矣。昔在 世宗朝传 教曰。王者之政。以安民为本。其要不越乎轻役薄赋而已。不急之敛。一皆停罢。以宽民力。庶副予仁恤元元之意。至于 世祖朝传 旨户曹曰。予尝念上之奉养过厚。故下之供亿难支。贻弊于民。其自今上自宫省。下至诸邑。一切经费。率皆定式。使民得免横敛。 殿下如欲体 二圣恤民薄敛之意。以致太平之治。诸道量案等第。次次而下。平均结数。宽其徭役。且于宫掖之中。损科外
无几。糊口艰乏。已不足说。而酬应各役。常患不给。故囚禁也刑杖也。百无一免。则用一缓二之政。固已左矣。而用三之政。必不过是。奚以免其殍。而能不至于父子之离耶。惟我 先王。念民饥馑。壬子初夏。特下霈恩。留其田租。用赈饥民。减其逋欠。以慰死亡。贫残缓收。各寺减捧。军保充定。退待三年。故民若解悬。鼓舞恩波。天心悔祸。甘澍霈然。天人感应。若是其速。而惟彼内外臣僚。不体 圣念之忧勤。谓其稍稔而两岁田税。一时俱收。且督逋欠。用殄馀民。诸邑军布。各寺贡物。奴婢身贡。并加苛刻。星火迫促。而京衙门军保。则充定之令尤急。乳下之孩。亦为勒定。则宋臣范镇所谓陛下有爱民之性。而大臣用残民之政者。不幸近之矣。昔在 世宗朝传 教曰。王者之政。以安民为本。其要不越乎轻役薄赋而已。不急之敛。一皆停罢。以宽民力。庶副予仁恤元元之意。至于 世祖朝传 旨户曹曰。予尝念上之奉养过厚。故下之供亿难支。贻弊于民。其自今上自宫省。下至诸邑。一切经费。率皆定式。使民得免横敛。 殿下如欲体 二圣恤民薄敛之意。以致太平之治。诸道量案等第。次次而下。平均结数。宽其徭役。且于宫掖之中。损科外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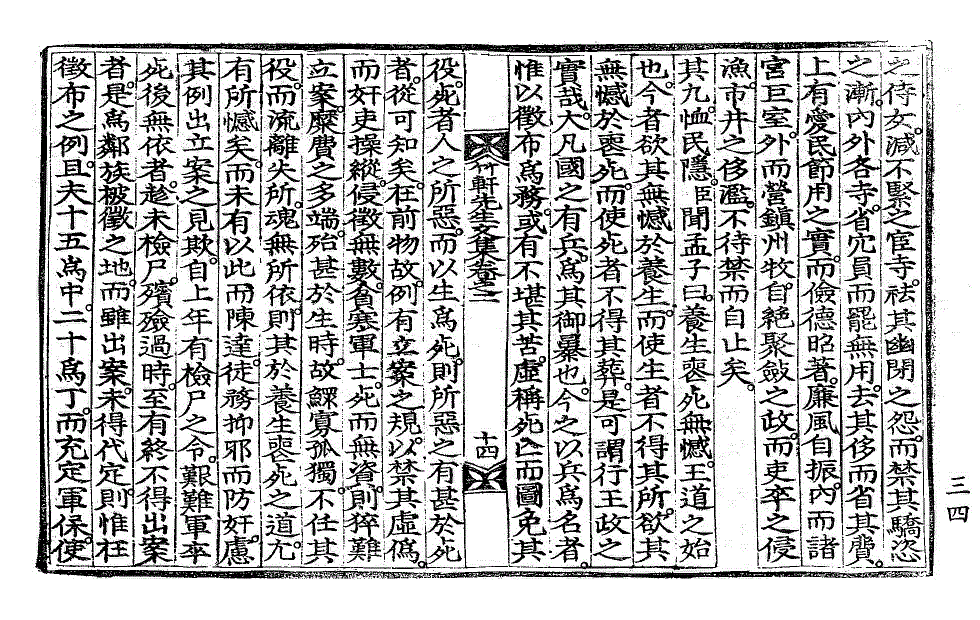 之侍女。减不紧之宦寺。祛其幽闭之怨。而禁其骄恣之渐。内外各寺。省冗员而罢无用。去其侈而省其费。上有爱民节用之实。而俭德昭著。廉风自振。内而诸宫巨室。外而营镇州牧。自绝聚敛之政。而吏卒之侵渔。市井之侈滥。不待禁而自止矣。
之侍女。减不紧之宦寺。祛其幽闭之怨。而禁其骄恣之渐。内外各寺。省冗员而罢无用。去其侈而省其费。上有爱民节用之实。而俭德昭著。廉风自振。内而诸宫巨室。外而营镇州牧。自绝聚敛之政。而吏卒之侵渔。市井之侈滥。不待禁而自止矣。[恤民隐]
其九。恤民隐。臣闻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今者欲其无憾于养生。而使生者不得其所。欲其无憾于丧死。而使死者不得其葬。是可谓行王政之实哉。大凡国之有兵。为其御㬥也。今之以兵为名者。惟以徵布为务。或有不堪其苦。虚称死亡而图免其役。死者人之所恶。而以生为死。则所恶之有甚于死者。从可知矣。在前物故。例有立案之规。以禁其虚伪。而奸吏操纵。侵徵无数。贫寒军士。死而无资。则猝难立案。糜费之多端。殆甚于生时。故鳏寡孤独。不任其役。而流离失所。魂无所依。则其于养生丧死之道。尤有所憾矣。而未有以此而陈达。徒务抑邪而防奸。虑其例出立案之见欺。自上年有检尸之令。艰难军卒死后无依者。趁未检尸。殡殓过时。至有终不得出案者。是为邻族被徵之地。而虽出案。未得代定。则惟在徵布之例。且夫十五为中。二十为丁。而充定军保。使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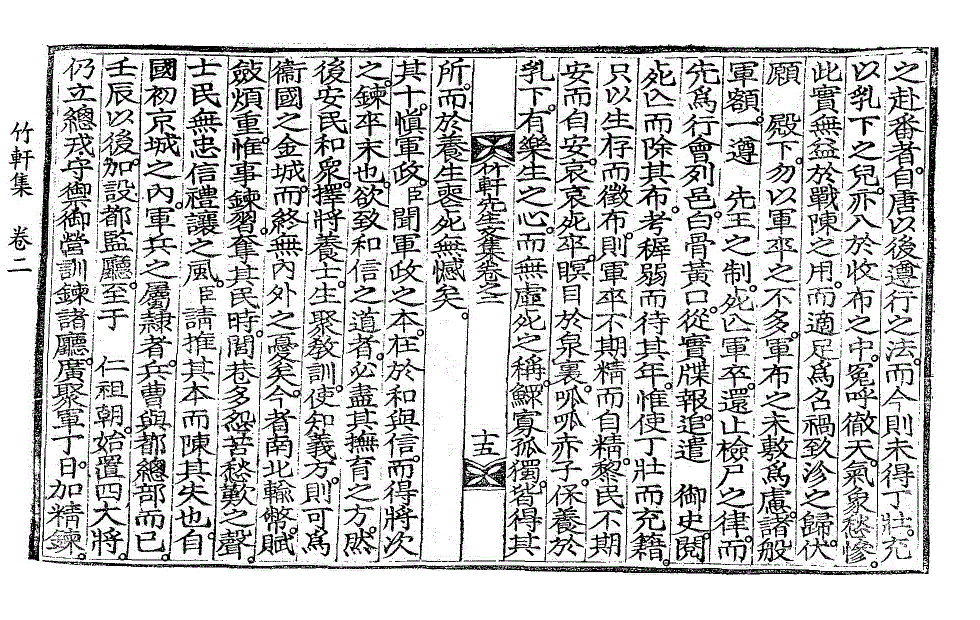 之赴番者。自唐以后遵行之法。而今则未得丁壮。充以乳下之儿。亦入于收布之中。冤呼彻天。气象愁惨。此实无益于战陈之用。而适足为名祸致沴之归。伏愿 殿下。勿以军卒之不多。军布之未敷为虑。诸般军额。一遵 先王之制。死亡军卒。还止检尸之律。而先为行会列邑。白骨黄口。从实牒报。追遣 御史。阅死亡而除其布。考稚弱而待其年。惟使丁壮而充籍。只以生存而徵布。则军卒不期精而自精。黎民不期安而自安。哀哀死卒。瞑目于泉里。呱呱赤子。保养于乳下。有乐生之心。而无虚死之称。鳏寡孤独。皆得其所。而于养生丧死无憾矣。
之赴番者。自唐以后遵行之法。而今则未得丁壮。充以乳下之儿。亦入于收布之中。冤呼彻天。气象愁惨。此实无益于战陈之用。而适足为名祸致沴之归。伏愿 殿下。勿以军卒之不多。军布之未敷为虑。诸般军额。一遵 先王之制。死亡军卒。还止检尸之律。而先为行会列邑。白骨黄口。从实牒报。追遣 御史。阅死亡而除其布。考稚弱而待其年。惟使丁壮而充籍。只以生存而徵布。则军卒不期精而自精。黎民不期安而自安。哀哀死卒。瞑目于泉里。呱呱赤子。保养于乳下。有乐生之心。而无虚死之称。鳏寡孤独。皆得其所。而于养生丧死无憾矣。[慎军政]
其十。慎军政。臣闻军政之本。在于和与信。而得将次之。鍊卒末也。欲致和信之道者。必尽其抚育之方。然后安民和众。择将养士。生聚教训。使知义方。则可为卫国之金城。而终无内外之忧矣。今者南北输币。赋敛烦重。惟事鍊习。夺其民时。闾巷多怨苦愁叹之声。士民无忠信礼让之风。臣请推其本而陈其失也。自国初京城之内。军兵之属隶者。兵曹与都总部而已。壬辰以后。加设都监厅。至于 仁祖朝。始置四大将。仍立总戎,守御,御营,训鍊诸厅。广聚军丁。日加精鍊。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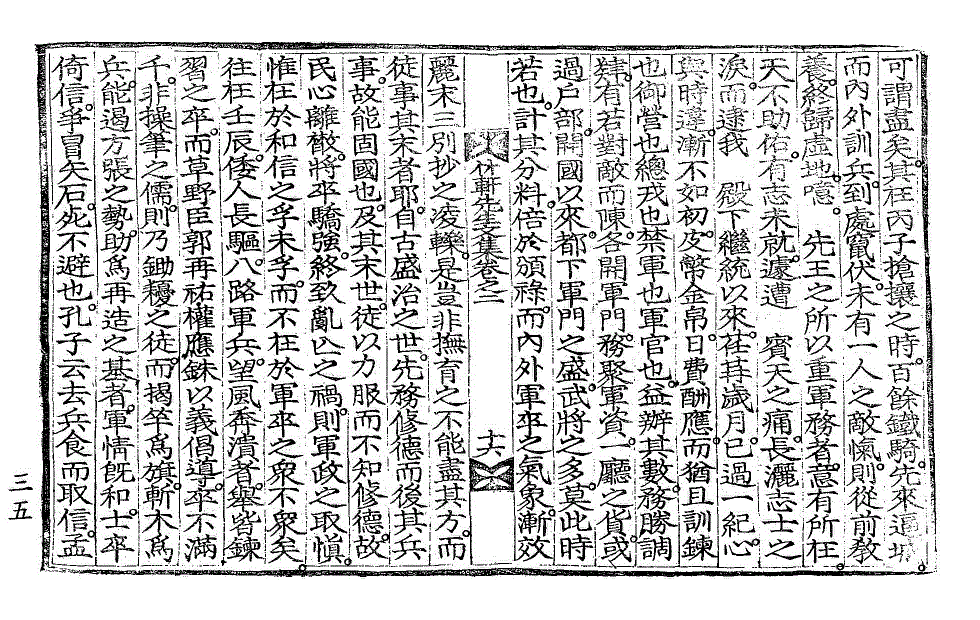 可谓尽矣。其在丙子抢攘之时。百馀铁骑。先来逼城。而内外训兵。到处窜伏。未有一人之敌忾。则从前教养。终归虚地。噫。 先王之所以重军务者。意有所在。天不助佑。有志未就。遽遭 宾天之痛。长洒志士之泪。而逮我 殿下继统以来。荏苒岁月。已过一纪。心与时违。渐不如初。皮币金帛。日费酬应。而犹且训鍊也御营也总戎也禁军也军官也。益办其数。务胜调肄。有若对敌而陈。各开军门。务聚军资。一厅之货。或过户部。开国以来。都下军门之盛。武将之多。莫此时若也。计其分料。倍于颁禄。而内外军卒之气象。渐效丽末三别抄之凌轹。是岂非抚育之不能尽其方。而徒事其末者耶。自古盛治之世。先务修德而后其兵事。故能固国也。及其末世。徒以力服而不知修德。故民心离散。将卒骄强。终致乱亡之祸。则军政之取慎。惟在于和信之孚未孚。而不在于军卒之众不众矣。往在壬辰。倭人长驱。八路军兵。望风奔溃者。举皆鍊习之卒。而草野臣郭再祐,权应铢以义倡导。卒不满千。非操笔之儒。则乃锄耰之徒。而揭竿为旗。斩木为兵。能遏方张之势。助为再造之基者。军情既和。士卒倚信。争冒失石。死不避也。孔子云去兵食而取信。孟
可谓尽矣。其在丙子抢攘之时。百馀铁骑。先来逼城。而内外训兵。到处窜伏。未有一人之敌忾。则从前教养。终归虚地。噫。 先王之所以重军务者。意有所在。天不助佑。有志未就。遽遭 宾天之痛。长洒志士之泪。而逮我 殿下继统以来。荏苒岁月。已过一纪。心与时违。渐不如初。皮币金帛。日费酬应。而犹且训鍊也御营也总戎也禁军也军官也。益办其数。务胜调肄。有若对敌而陈。各开军门。务聚军资。一厅之货。或过户部。开国以来。都下军门之盛。武将之多。莫此时若也。计其分料。倍于颁禄。而内外军卒之气象。渐效丽末三别抄之凌轹。是岂非抚育之不能尽其方。而徒事其末者耶。自古盛治之世。先务修德而后其兵事。故能固国也。及其末世。徒以力服而不知修德。故民心离散。将卒骄强。终致乱亡之祸。则军政之取慎。惟在于和信之孚未孚。而不在于军卒之众不众矣。往在壬辰。倭人长驱。八路军兵。望风奔溃者。举皆鍊习之卒。而草野臣郭再祐,权应铢以义倡导。卒不满千。非操笔之儒。则乃锄耰之徒。而揭竿为旗。斩木为兵。能遏方张之势。助为再造之基者。军情既和。士卒倚信。争冒失石。死不避也。孔子云去兵食而取信。孟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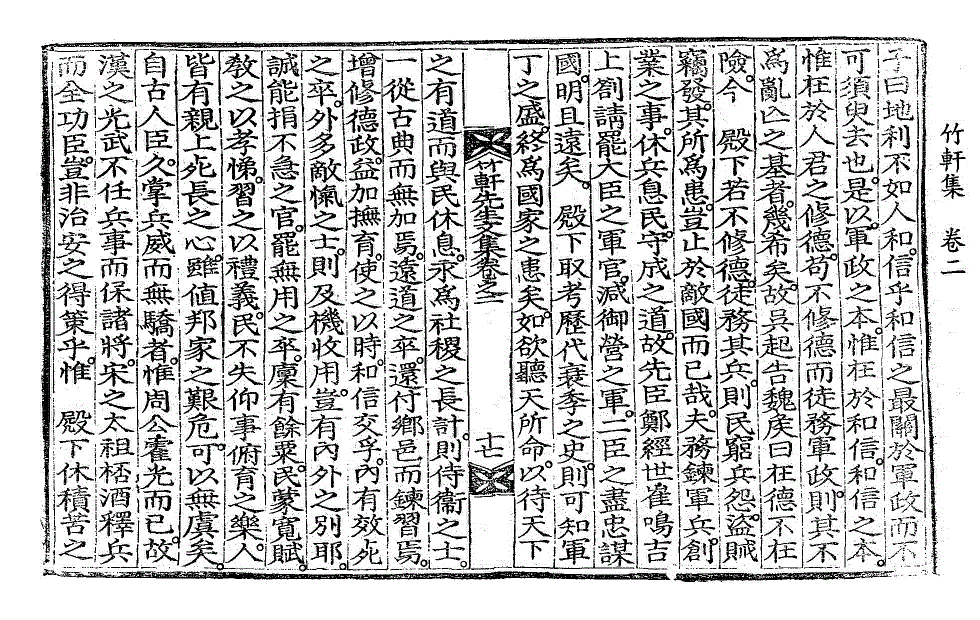 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信乎和信之最关于军政而不可须臾去也。是以。军政之本。惟在于和信。和信之本。惟在于人君之修德。苟不修德而徒务军政。则其不为乱亡之基者。几希矣。故吴起告魏侯曰在德不在险。今 殿下若不修德。徒务其兵。则民穷兵怨。盗贼窃发。其所为患。岂止于敌国而已哉。夫务鍊军兵。创业之事。休兵息民。守成之道。故先臣郑经世,崔鸣吉上劄请罢大臣之军官。减御营之军。二臣之尽忠谋国。明且远矣。 殿下取考历代衰季之史。则可知军丁之盛。终为国家之患矣。如欲听天所命。以待天下之有道而与民休息。永为社稷之长计。则侍卫之士。一从古典而无加焉。远道之卒。还付乡邑而鍊习焉。增修德政。益加抚育。使之以时。和信交孚。内有效死之卒。外多敌忾之士。则及机收用。岂有内外之别耶。诚能捐不急之官。罢无用之卒。廪有馀粟。民蒙宽赋。教之以孝悌。习之以礼义。民不失仰事俯育之乐。人皆有亲上死长之心。虽值邦家之艰危。可以无虞矣。自古人臣。久掌兵威而无骄者。惟周公,霍光而已。故汉之光武不任兵事而保诸将。宋之太祖杯酒释兵而全功臣。岂非治安之得策乎。惟 殿下休积苦之
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信乎和信之最关于军政而不可须臾去也。是以。军政之本。惟在于和信。和信之本。惟在于人君之修德。苟不修德而徒务军政。则其不为乱亡之基者。几希矣。故吴起告魏侯曰在德不在险。今 殿下若不修德。徒务其兵。则民穷兵怨。盗贼窃发。其所为患。岂止于敌国而已哉。夫务鍊军兵。创业之事。休兵息民。守成之道。故先臣郑经世,崔鸣吉上劄请罢大臣之军官。减御营之军。二臣之尽忠谋国。明且远矣。 殿下取考历代衰季之史。则可知军丁之盛。终为国家之患矣。如欲听天所命。以待天下之有道而与民休息。永为社稷之长计。则侍卫之士。一从古典而无加焉。远道之卒。还付乡邑而鍊习焉。增修德政。益加抚育。使之以时。和信交孚。内有效死之卒。外多敌忾之士。则及机收用。岂有内外之别耶。诚能捐不急之官。罢无用之卒。廪有馀粟。民蒙宽赋。教之以孝悌。习之以礼义。民不失仰事俯育之乐。人皆有亲上死长之心。虽值邦家之艰危。可以无虞矣。自古人臣。久掌兵威而无骄者。惟周公,霍光而已。故汉之光武不任兵事而保诸将。宋之太祖杯酒释兵而全功臣。岂非治安之得策乎。惟 殿下休积苦之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6L 页
 士而防未然之微。罢虚劳之将而杜骄强之渐。效光武之沈几。非警急不言兵。体周宣之内修。任其将养其兵。则国有磐石之安。边无刁斗之警矣。内乱何从而起哉。外患何由而至哉。当今国家之势。虽若无目前之患。祸乱之几。有可虞者。无事而劳众。兵之怨极矣。无用而聚货。民之困极矣。有一于斯。足以招灾。况并行者乎。语曰。物极则反。治至则危。以此推之。慎厥军政。此其时也。 殿下试以臣言下询于大臣与诸将。则亦必明其几而尽其辞矣。伏愿自今君臣上下。共务和信之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以安家国。以幸万世。
士而防未然之微。罢虚劳之将而杜骄强之渐。效光武之沈几。非警急不言兵。体周宣之内修。任其将养其兵。则国有磐石之安。边无刁斗之警矣。内乱何从而起哉。外患何由而至哉。当今国家之势。虽若无目前之患。祸乱之几。有可虞者。无事而劳众。兵之怨极矣。无用而聚货。民之困极矣。有一于斯。足以招灾。况并行者乎。语曰。物极则反。治至则危。以此推之。慎厥军政。此其时也。 殿下试以臣言下询于大臣与诸将。则亦必明其几而尽其辞矣。伏愿自今君臣上下。共务和信之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以安家国。以幸万世。[察军情]
其十一。察军情。臣闻国之有兵。为其御敌也。兵之有将。为其教训也。陆军则使兵使而主之。水军则使水使而主之。有正军焉。有保人焉。正军则随将而分番。学习战艺。保人则出粟布以助正军。乃 先王为国寘兵之意也。而世降俗下。为将者唯知逐名收布。而不知合变之为何事。为兵者唯知备纳番布。而不知弓剑之为何技。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及其有变。驱其不教之民。使之赴敌。未接兵刃。望风奔溃。求厥所由。非将之罪也。乃国家待将之非其道也。何以言之。边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7H 页
 阃国之重镇也。许多军务。各项酬用。实与邑宰县官。大小相悬。而月廪之外。无佗资用。使之专责于防军。故屯租也役价也后木也。从马之木。冰丁之布。计名而收捧。不独徵布于正军。保人价布。并为收捧。而犹以为不足。称以贸易。恣意徵敛。一名所纳。各浦则三匹。兵营则二匹。而贸易之数。或至倍蓰。一岁一番。犹且不堪。再赴兵营。保存无几。而逃故虚簿。随岁充定。良家之子。未学呼爷。已先案簿。一室之内。以男为名者。不较老弱。率皆徵布。而逃故番布。亦及邻族。是故。名编军案。视若归死。哀哉军丁。独非王民。且夫战亡后裔。有荫子孙。欲免番布之苦。图得忠赞卫忠壮卫等口传。则移属射夫。只徵二匹。以是为幸。而前日华使之来。名以助粮。收常木一匹。乃者敕使重叠。国贮未给。称以扶助。各收细木半匹。自此之后。未有还止之令。故岁徵一匹。已成其规。荫职之布。还有甚于防军。法之不信。为如何哉。非止此也。本司之吏。以此为奇货。上番之流有故者。则自本官报颐者。乃是例也。而胥吏则唯肆其巧。主司则唯谨其署。推责兵使。拿致营吏。领诣京司而点颐。则非但远路之费。且徵未到之罚。其为糜费。难以纪极。而或亲自赴番。则百尔
阃国之重镇也。许多军务。各项酬用。实与邑宰县官。大小相悬。而月廪之外。无佗资用。使之专责于防军。故屯租也役价也后木也。从马之木。冰丁之布。计名而收捧。不独徵布于正军。保人价布。并为收捧。而犹以为不足。称以贸易。恣意徵敛。一名所纳。各浦则三匹。兵营则二匹。而贸易之数。或至倍蓰。一岁一番。犹且不堪。再赴兵营。保存无几。而逃故虚簿。随岁充定。良家之子。未学呼爷。已先案簿。一室之内。以男为名者。不较老弱。率皆徵布。而逃故番布。亦及邻族。是故。名编军案。视若归死。哀哉军丁。独非王民。且夫战亡后裔。有荫子孙。欲免番布之苦。图得忠赞卫忠壮卫等口传。则移属射夫。只徵二匹。以是为幸。而前日华使之来。名以助粮。收常木一匹。乃者敕使重叠。国贮未给。称以扶助。各收细木半匹。自此之后。未有还止之令。故岁徵一匹。已成其规。荫职之布。还有甚于防军。法之不信。为如何哉。非止此也。本司之吏。以此为奇货。上番之流有故者。则自本官报颐者。乃是例也。而胥吏则唯肆其巧。主司则唯谨其署。推责兵使。拿致营吏。领诣京司而点颐。则非但远路之费。且徵未到之罚。其为糜费。难以纪极。而或亲自赴番。则百尔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7L 页
 沮戏。使不立番。必捧二匹番布。吏取其半。及其放还之后。追送阙番之关。中间责应之烦。千里往来之苦。有倍于贱卒。故有荫之类。图隐其父祖之录券。臣恐藩屏之士。以是而莫肯向敌争死耳。且御营之军。当其编束之初。鼓舞乐簿。而今则徵布保人。输诸本司。则亦有怨苦之心。抑未知各衙门军布之收敛者。计数而输之于国家之用耶。丁壮之名簿军案者。在外则付诸镇营。恣其徵敛。在内则委诸下吏。肆其虚费。而聚朝东暮西之辈。称以束伍。倚以为重。而主将与将官。惟以棍杖而立威。使之坐作进退。则俱是锄耰之类。未专于兵农。终岁勤苦。而不见甔石之资。间或试艺。而未谙放射之法。身无被坚。手无执锐。而使之赴敌。则其于亲上死长之义。奚暇念及哉。邦家树兵。本非为布。而今为谬规。犹不堪徵。而重以助布之令。贪虐之徒。更复因缘。恣行侵㬥。益肆诛求。则剥肤椎髓。为患益甚矣。惟 殿下首破谬规。荡涤未收之布。正军则择其勇健者。为之而学习战艺。保人则助农正军而除其番布。助其战具。民之愿为正军。有若登科者然。则何患于战陈而无勇耶。事大之礼。在所不已。而助粮之有补于敕使之费。终不可废也。则何不
沮戏。使不立番。必捧二匹番布。吏取其半。及其放还之后。追送阙番之关。中间责应之烦。千里往来之苦。有倍于贱卒。故有荫之类。图隐其父祖之录券。臣恐藩屏之士。以是而莫肯向敌争死耳。且御营之军。当其编束之初。鼓舞乐簿。而今则徵布保人。输诸本司。则亦有怨苦之心。抑未知各衙门军布之收敛者。计数而输之于国家之用耶。丁壮之名簿军案者。在外则付诸镇营。恣其徵敛。在内则委诸下吏。肆其虚费。而聚朝东暮西之辈。称以束伍。倚以为重。而主将与将官。惟以棍杖而立威。使之坐作进退。则俱是锄耰之类。未专于兵农。终岁勤苦。而不见甔石之资。间或试艺。而未谙放射之法。身无被坚。手无执锐。而使之赴敌。则其于亲上死长之义。奚暇念及哉。邦家树兵。本非为布。而今为谬规。犹不堪徵。而重以助布之令。贪虐之徒。更复因缘。恣行侵㬥。益肆诛求。则剥肤椎髓。为患益甚矣。惟 殿下首破谬规。荡涤未收之布。正军则择其勇健者。为之而学习战艺。保人则助农正军而除其番布。助其战具。民之愿为正军。有若登科者然。则何患于战陈而无勇耶。事大之礼。在所不已。而助粮之有补于敕使之费。终不可废也。则何不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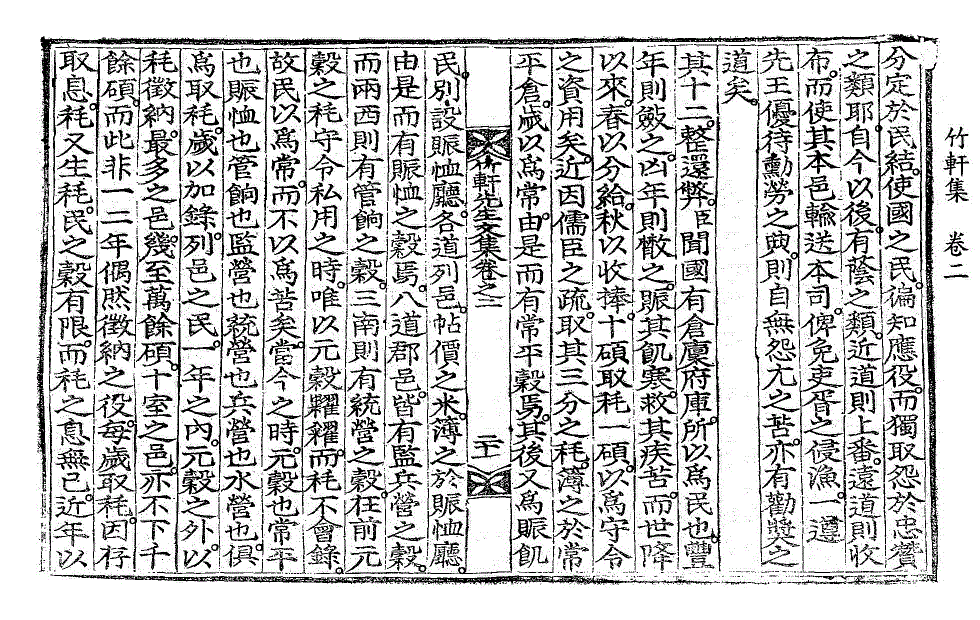 分定于民结。使国之民。遍知应役。而独取怨于忠赞之类耶。自今以后。有荫之类。近道则上番。远道则收布。而使其本邑输送本司。俾免吏胥之侵渔。一遵 先王优待勋劳之典。则自无怨尤之苦。亦有劝奖之道矣。
分定于民结。使国之民。遍知应役。而独取怨于忠赞之类耶。自今以后。有荫之类。近道则上番。远道则收布。而使其本邑输送本司。俾免吏胥之侵渔。一遵 先王优待勋劳之典。则自无怨尤之苦。亦有劝奖之道矣。[整还弊]
其十二。整还弊。臣闻国有仓廪府库。所以为民也。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赈其饥寒。救其疾苦。而世降以来。春以分给。秋以收捧。十硕取秏一硕。以为守令之资用矣。近因儒臣之疏。取其三分之秏。簿之于常平仓。岁以为常。由是而有常平谷焉。其后又为赈饥民。别设赈恤厅。各道列邑。帖价之米。簿之于赈恤厅。由是而有赈恤之谷焉。八道郡邑。皆有监兵营之谷。而两西则有管饷之谷。三南则有统营之谷。在前元谷之秏守令私用之时。唯以元谷粜籴。而秏不会录。故民以为常。而不以为苦矣。当今之时。元谷也常平也赈恤也管饷也监营也统营也丘营也水营也。俱为取秏。岁以加录。列邑之民。一年之内。元谷之外。以秏徵纳。最多之邑。几至万馀硕。十室之邑。亦不下千馀硕。而此非一二年偶然徵纳之役。每岁取秏。因存取息。秏又生秏。民之谷有限。而秏之息无已。近年以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8L 页
 来。累岁不登。贫寒之民。惟知受食而无路备纳。多者或过百馀硕。少者亦至五六十硕。虽加酷刑。终无所纳。则列邑守令。图免己罪。瞒报毕捧。仍为秩反。其来已久。则虽或有荡涤之恩。既入于已捧之数。故不得均蒙其惠。逐年出秏。其息愈多。八口之家。终岁勤苦。备纳元谷。常患不足。卒岁延命。只是橡栗菜叶。而邻族逋欠。又从而徵催科政。严吏尚苛酷。系脰束手。相及于路。连衽贯索。有似俘虏。昼处冻地。逐日受刑。夜闭冷狱。与鬼为邻。或有经春牢囚。逢夏始放。仍致失业。每当秋冬。村闾萧然。若经兵革。气像愁惨。其所以为民之良法。反为剥民之虐政。则今之民瘼。此为第一。而所谓常平仓。非耿寿昌便民之意。所谓赈恤谷。无汲黯发赈之举。而其中管饷之谷。虽曰小有补于国用。犹是割肉充腹。至于三营及各邑之取秏。有何益于国家也。营镇各邑。俱有所供之需。而其中统营。则非徒收布于八船之防军。且有添防之助营下之谷累钜万。而屯军募军之备纳军饷者。遍在近邑。其数不赀。营底居民五六千。而几半贸谷之军。春秋贾贩。百种搜罗。而专获海错。以资需用。则不待外输而可以周给矣。若使防其酬应之烦而库有馀财。省其
来。累岁不登。贫寒之民。惟知受食而无路备纳。多者或过百馀硕。少者亦至五六十硕。虽加酷刑。终无所纳。则列邑守令。图免己罪。瞒报毕捧。仍为秩反。其来已久。则虽或有荡涤之恩。既入于已捧之数。故不得均蒙其惠。逐年出秏。其息愈多。八口之家。终岁勤苦。备纳元谷。常患不足。卒岁延命。只是橡栗菜叶。而邻族逋欠。又从而徵催科政。严吏尚苛酷。系脰束手。相及于路。连衽贯索。有似俘虏。昼处冻地。逐日受刑。夜闭冷狱。与鬼为邻。或有经春牢囚。逢夏始放。仍致失业。每当秋冬。村闾萧然。若经兵革。气像愁惨。其所以为民之良法。反为剥民之虐政。则今之民瘼。此为第一。而所谓常平仓。非耿寿昌便民之意。所谓赈恤谷。无汲黯发赈之举。而其中管饷之谷。虽曰小有补于国用。犹是割肉充腹。至于三营及各邑之取秏。有何益于国家也。营镇各邑。俱有所供之需。而其中统营。则非徒收布于八船之防军。且有添防之助营下之谷累钜万。而屯军募军之备纳军饷者。遍在近邑。其数不赀。营底居民五六千。而几半贸谷之军。春秋贾贩。百种搜罗。而专获海错。以资需用。则不待外输而可以周给矣。若使防其酬应之烦而库有馀财。省其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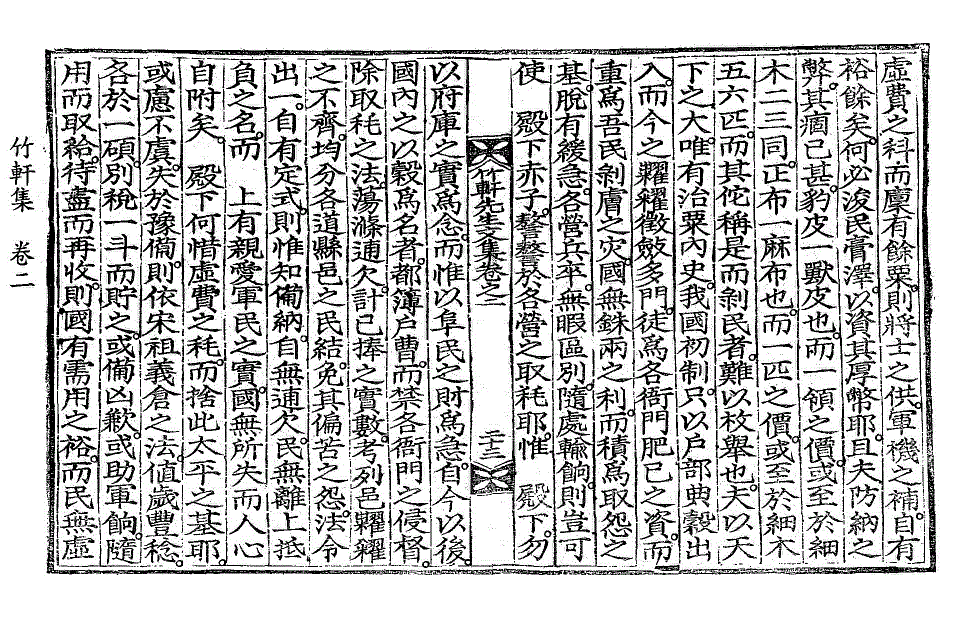 虚费之科而廪有馀粟。则将士之供。军机之补。自有裕馀矣。何必浚民膏泽。以资其厚币耶。且夫防纳之弊。其痼已甚。豹皮一兽皮也。而一领之价。或至于细木二三同。正布一麻布也。而一匹之价。或至于细木五六匹。而其佗称是而剥民者。难以枚举也。夫以天下之大。唯有治粟内史。我国初制。只以户部典谷出入。而今之粜籴徵敛多门。徒为各衙门肥己之资。而重为吾民剥肤之灾。国无铢两之利。而积为取怨之基。脱有缓急。各营兵卒。无暇区别。随处输饷。则岂可使 殿下赤子。謷謷于各营之取秏耶。惟 殿下。勿以府库之实为念。而惟以阜民之财为急。自今以后。国内之以谷为名者。都簿户曹。而禁各衙门之侵督。除取秏之法。荡涤逋欠。计已捧之实数。考列邑粜籴之不齐。均分各道县邑之民结。免其偏苦之怨。法令出一。自有定式。则惟知备纳。自无逋欠。民无离上抵负之名。而 上有亲爱军民之实。国无所失而人心自附矣。 殿下何惜虚费之秏。而舍此太平之基耶。或虑不虞。失于豫备。则依宋祖义仓之法。值岁丰稔。各于一硕。别税一斗而贮之。或备凶歉。或助军饷。随用而取给。待尽而再收。则国有需用之裕。而民无虚
虚费之科而廪有馀粟。则将士之供。军机之补。自有裕馀矣。何必浚民膏泽。以资其厚币耶。且夫防纳之弊。其痼已甚。豹皮一兽皮也。而一领之价。或至于细木二三同。正布一麻布也。而一匹之价。或至于细木五六匹。而其佗称是而剥民者。难以枚举也。夫以天下之大。唯有治粟内史。我国初制。只以户部典谷出入。而今之粜籴徵敛多门。徒为各衙门肥己之资。而重为吾民剥肤之灾。国无铢两之利。而积为取怨之基。脱有缓急。各营兵卒。无暇区别。随处输饷。则岂可使 殿下赤子。謷謷于各营之取秏耶。惟 殿下。勿以府库之实为念。而惟以阜民之财为急。自今以后。国内之以谷为名者。都簿户曹。而禁各衙门之侵督。除取秏之法。荡涤逋欠。计已捧之实数。考列邑粜籴之不齐。均分各道县邑之民结。免其偏苦之怨。法令出一。自有定式。则惟知备纳。自无逋欠。民无离上抵负之名。而 上有亲爱军民之实。国无所失而人心自附矣。 殿下何惜虚费之秏。而舍此太平之基耶。或虑不虞。失于豫备。则依宋祖义仓之法。值岁丰稔。各于一硕。别税一斗而贮之。或备凶歉。或助军饷。随用而取给。待尽而再收。则国有需用之裕。而民无虚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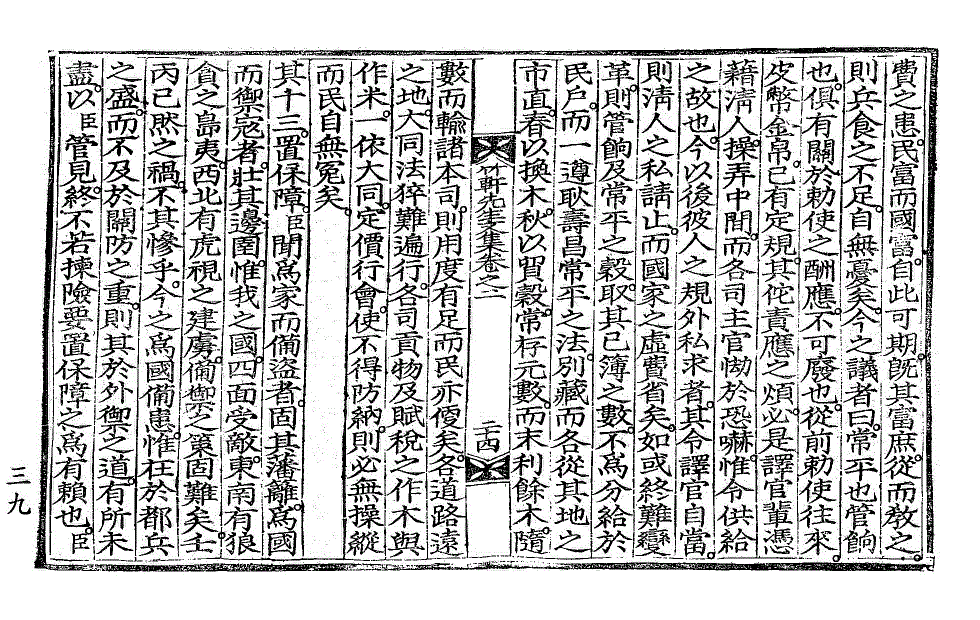 费之患。民富而国富。自此可期。既其富庶。从而教之。则兵食之不足。自无忧矣。今之议者曰。常平也管饷也。俱有关于敕使之酬应。不可废也。从前敕使往来。皮币金帛。已有定规。其佗责应之烦。必是译官辈凭藉清人。操弄中间。而各司主官㤼于恐吓。惟令供给之故也。今以后彼人之规外私求者。其令译官自当。则清人之私请止。而国家之虚费省矣。如或终难变革。则管饷及常平之谷。取其已簿之数。不为分给于民户。而一遵耿寿昌常平之法。别藏而各从其地之市直。春以换木。秋以贸谷。常存元数。而末利馀木。随数而输诸本司。则用度有足而民亦便矣。各道路远之地。大同法猝难遍行。各司贡物及赋税之作木与作米。一依大同。定价行会。使不得防纳。则必无操纵而民自无冤矣。
费之患。民富而国富。自此可期。既其富庶。从而教之。则兵食之不足。自无忧矣。今之议者曰。常平也管饷也。俱有关于敕使之酬应。不可废也。从前敕使往来。皮币金帛。已有定规。其佗责应之烦。必是译官辈凭藉清人。操弄中间。而各司主官㤼于恐吓。惟令供给之故也。今以后彼人之规外私求者。其令译官自当。则清人之私请止。而国家之虚费省矣。如或终难变革。则管饷及常平之谷。取其已簿之数。不为分给于民户。而一遵耿寿昌常平之法。别藏而各从其地之市直。春以换木。秋以贸谷。常存元数。而末利馀木。随数而输诸本司。则用度有足而民亦便矣。各道路远之地。大同法猝难遍行。各司贡物及赋税之作木与作米。一依大同。定价行会。使不得防纳。则必无操纵而民自无冤矣。[置保障]
其十三。置保障。臣闻为家而备盗者。固其藩篱。为国而御寇者。壮其边圉。惟我之国。四面受敌。东南有狼贪之岛夷。西北有虎视之建虏。备御之策固难矣。壬丙已然之祸。不其惨乎。今之为国备患。惟在于都兵之盛。而不及于关防之重。则其于外御之道。有所未尽。以臣管见。终不若拣险要置保障之为有赖也。臣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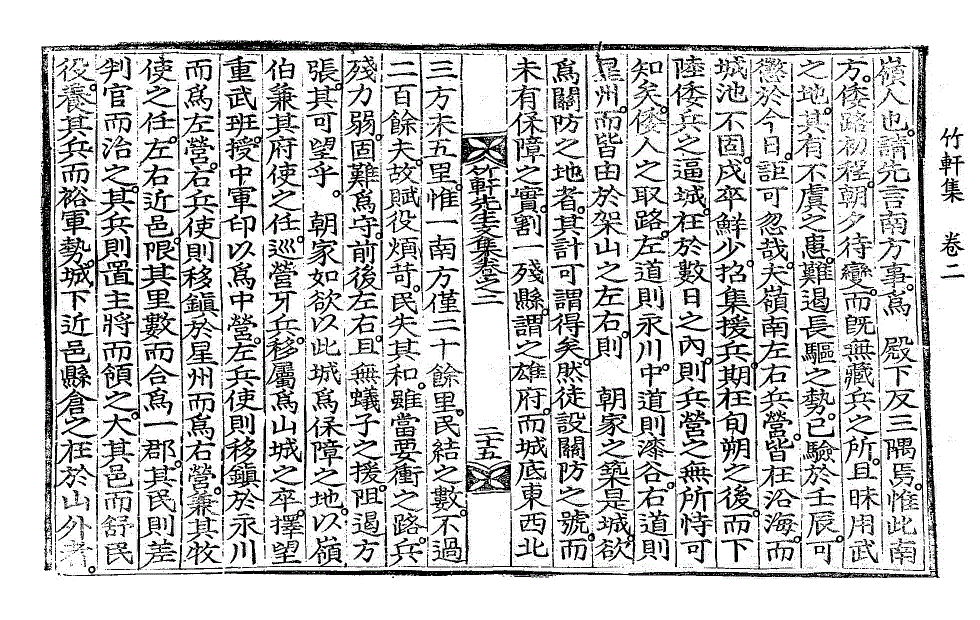 岭人也。请先言南方事。为 殿下反三隅焉。惟此南方。倭路初程。朝夕待变。而既无藏兵之所。且昧用武之地。其有不虞之患。难遏长驱之势。已验于壬辰。可惩于今日。讵可忽哉。夫岭南左右兵营。皆在沿海。而城池不固。戍卒鲜少。招集援兵。期在旬朔之后。而下陆倭兵之逼城。在于数日之内。则兵营之无所恃可知矣。倭人之取路。左道则永川。中道则漆谷。右道则星州。而皆由于架山之左右。则 朝家之筑是城。欲为关防之地者。其计可谓得矣。然徒设关防之号。而未有保障之实。割一残县。谓之雄府。而城底东西北三方未五里。惟一南方仅二十馀里。民结之数。不过二百馀夫。故赋役烦苛。民失其和。虽当要冲之路。兵残力弱。固难为守。前后左右。且无蚁子之援。阻遏方张。其可望乎。 朝家如欲以此城为保障之地。以岭伯兼其府使之任。巡营牙兵。移属为山城之卒。择望重武班。援中军印以为中营。左兵使则移镇于永川而为左营。右兵使则移镇于星州而为右营。兼其牧使之任。左右近邑。限其里数而合为一郡。其民则差判官而治之。其兵则置主将而领之。大其邑而舒民役。养其兵而裕军势。城下近邑县仓之在于山外者。
岭人也。请先言南方事。为 殿下反三隅焉。惟此南方。倭路初程。朝夕待变。而既无藏兵之所。且昧用武之地。其有不虞之患。难遏长驱之势。已验于壬辰。可惩于今日。讵可忽哉。夫岭南左右兵营。皆在沿海。而城池不固。戍卒鲜少。招集援兵。期在旬朔之后。而下陆倭兵之逼城。在于数日之内。则兵营之无所恃可知矣。倭人之取路。左道则永川。中道则漆谷。右道则星州。而皆由于架山之左右。则 朝家之筑是城。欲为关防之地者。其计可谓得矣。然徒设关防之号。而未有保障之实。割一残县。谓之雄府。而城底东西北三方未五里。惟一南方仅二十馀里。民结之数。不过二百馀夫。故赋役烦苛。民失其和。虽当要冲之路。兵残力弱。固难为守。前后左右。且无蚁子之援。阻遏方张。其可望乎。 朝家如欲以此城为保障之地。以岭伯兼其府使之任。巡营牙兵。移属为山城之卒。择望重武班。援中军印以为中营。左兵使则移镇于永川而为左营。右兵使则移镇于星州而为右营。兼其牧使之任。左右近邑。限其里数而合为一郡。其民则差判官而治之。其兵则置主将而领之。大其邑而舒民役。养其兵而裕军势。城下近邑县仓之在于山外者。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0L 页
 移设于城底五里之内。则足食足兵。亦一道也。惟此三大镇。鼎峙于三路之要冲。互为辅车之势。而架山城头。頫视敌兵之所向。邀击利钝。昭在目中。不待探报。可以相援。永川与架山相距五十里。星州与架山相距亦五十里。而金乌与天生两城。列峙其间。海寇所由之三路。初虽歧分。而终归于架山之下。山崎路险。旁多深谷。皆可以藏兵而遮绝。山回水阻。地便用武。亦可以游兵而掩杀。此所谓金城汤池也。贼由中道。则中营为前军而左右营翼之。贼由左路。则左营为前军而中营翼之。右营游击焉。贼由右路。则右营为前军而中营翼之。左营游击焉。平原坦道。则设兵车而制之。崎岖狭路。则多置疑兵于山上。设伏炮弩于谷口。据险待敌。以一当百。此之谓也。贼兵虽盛。必不后此三镇而径进。若欲屠此三镇而后已。则蚌鹬相持。禁其冲突有馀矣。庆州,金海,晋州,大丘之营将。其于方张之贼锋。势难独遏。则且战且退。来陈于三镇间要害之处。尚州之镇。来陈于金乌城。安东之镇。来陈于天生城。各据要路。以为内外唇齿之势。阻遏贼锋。自朝廷分付诸道。把守要路。则三镇以北。可以奠枕而作农矣。巧倭若知此形势而避之。取路湖南。
移设于城底五里之内。则足食足兵。亦一道也。惟此三大镇。鼎峙于三路之要冲。互为辅车之势。而架山城头。頫视敌兵之所向。邀击利钝。昭在目中。不待探报。可以相援。永川与架山相距五十里。星州与架山相距亦五十里。而金乌与天生两城。列峙其间。海寇所由之三路。初虽歧分。而终归于架山之下。山崎路险。旁多深谷。皆可以藏兵而遮绝。山回水阻。地便用武。亦可以游兵而掩杀。此所谓金城汤池也。贼由中道。则中营为前军而左右营翼之。贼由左路。则左营为前军而中营翼之。右营游击焉。贼由右路。则右营为前军而中营翼之。左营游击焉。平原坦道。则设兵车而制之。崎岖狭路。则多置疑兵于山上。设伏炮弩于谷口。据险待敌。以一当百。此之谓也。贼兵虽盛。必不后此三镇而径进。若欲屠此三镇而后已。则蚌鹬相持。禁其冲突有馀矣。庆州,金海,晋州,大丘之营将。其于方张之贼锋。势难独遏。则且战且退。来陈于三镇间要害之处。尚州之镇。来陈于金乌城。安东之镇。来陈于天生城。各据要路。以为内外唇齿之势。阻遏贼锋。自朝廷分付诸道。把守要路。则三镇以北。可以奠枕而作农矣。巧倭若知此形势而避之。取路湖南。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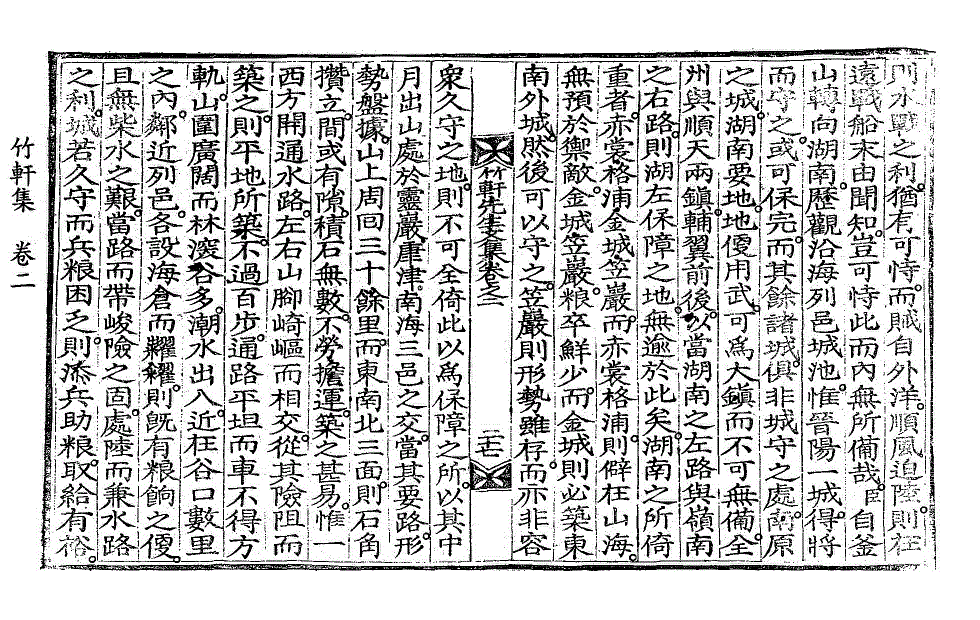 则水战之利。犹有可恃。而贼自外洋。顺风迫陆。则在远战船末由闻知。岂可恃此而内无所备哉。臣自釜山转向湖南。历观沿海列邑城池。惟晋阳一城。得将而守之。或可保完。而其馀诸城。俱非城守之处。南原之城。湖南要地。地便用武。可为大镇而不可无备。全州与顺天两镇。辅翼前后。以当湖南之左路与岭南之右路。则湖左保障之地。无逾于此矣。湖南之所倚重者。赤裳,格浦,金城,笠岩。而赤裳格浦。则僻在山海。无预于御敌。金城,笠岩。粮卒鲜少。而金城则必筑东南外城。然后可以守之。笠岩则形势虽存。而亦非容众久守之地。则不可全倚此以为保障之所。以其中月出山处于灵岩,康津,南海三邑之交。当其要路。形势盘据。山上周回三十馀里。而东南北三面。则石角攒立。间或有隙。积石无数。不劳担运。筑之甚易。惟一西方开通水路。左右山脚崎岖而相交。从其险阻而筑之。则平地所筑。不过百步。通路平坦而车不得方轨。山围广阔而林深谷多。潮水出入。近在谷口数里之内。邻近列邑。各设海仓而粜籴。则既有粮饷之便。且无柴水之艰。当路而带峻险之固。处陆而兼水路之利。城若久守而兵粮困乏。则添兵助粮。取给有裕。
则水战之利。犹有可恃。而贼自外洋。顺风迫陆。则在远战船末由闻知。岂可恃此而内无所备哉。臣自釜山转向湖南。历观沿海列邑城池。惟晋阳一城。得将而守之。或可保完。而其馀诸城。俱非城守之处。南原之城。湖南要地。地便用武。可为大镇而不可无备。全州与顺天两镇。辅翼前后。以当湖南之左路与岭南之右路。则湖左保障之地。无逾于此矣。湖南之所倚重者。赤裳,格浦,金城,笠岩。而赤裳格浦。则僻在山海。无预于御敌。金城,笠岩。粮卒鲜少。而金城则必筑东南外城。然后可以守之。笠岩则形势虽存。而亦非容众久守之地。则不可全倚此以为保障之所。以其中月出山处于灵岩,康津,南海三邑之交。当其要路。形势盘据。山上周回三十馀里。而东南北三面。则石角攒立。间或有隙。积石无数。不劳担运。筑之甚易。惟一西方开通水路。左右山脚崎岖而相交。从其险阻而筑之。则平地所筑。不过百步。通路平坦而车不得方轨。山围广阔而林深谷多。潮水出入。近在谷口数里之内。邻近列邑。各设海仓而粜籴。则既有粮饷之便。且无柴水之艰。当路而带峻险之固。处陆而兼水路之利。城若久守而兵粮困乏。则添兵助粮。取给有裕。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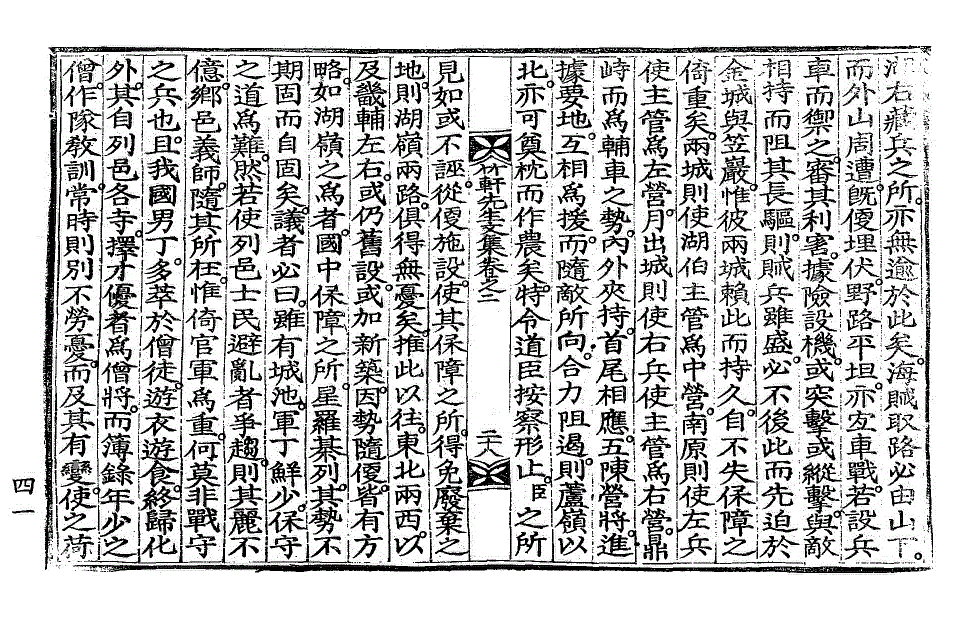 湖右藏兵之所。亦无逾于此矣。海贼取路必由山下。而外山周遭。既便埋伏。野路平坦。亦宜车战。若设兵车而御之。审其利害。据险设机。或突击或纵击。与敌相持而阻其长驱。则贼兵虽盛。必不后此而先迫于金城与笠岩。惟彼两城赖此而持久。自不失保障之倚重矣。两城则使湖伯主管为中营。南原则使左兵使主管为左营。月出城则使右兵使主管为右营。鼎峙而为转车之势。内外夹持。首尾相应。五陈营将。进据要地。互相为援。而随敌所向。合力阻遏。则芦岭以北。亦可奠枕而作农矣。特令道臣按察形止。臣之所见如或不诬。从便施设。使其保障之所。得免废弃之地。则湖岭两路。俱得无忧矣。推此以往。东北两西。以及畿辅左右。或仍旧设。或加新筑。因势随便。皆有方略。如湖岭之为者。国中保障之所。星罗棋列。其势不期固而自固矣。议者必曰。虽有城池。军丁鲜少。保守之道为难。然若使列邑士民避乱者争趋。则其丽不亿。乡邑义师。随其所在。惟倚官军为重。何莫非战守之兵也。且我国男丁。多萃于僧徒。游衣游食。终归化外。其自列邑各寺。择才优者为僧将。而簿录年少之僧。作队教训。常时则别不劳忧。而及其有变。使之荷
湖右藏兵之所。亦无逾于此矣。海贼取路必由山下。而外山周遭。既便埋伏。野路平坦。亦宜车战。若设兵车而御之。审其利害。据险设机。或突击或纵击。与敌相持而阻其长驱。则贼兵虽盛。必不后此而先迫于金城与笠岩。惟彼两城赖此而持久。自不失保障之倚重矣。两城则使湖伯主管为中营。南原则使左兵使主管为左营。月出城则使右兵使主管为右营。鼎峙而为转车之势。内外夹持。首尾相应。五陈营将。进据要地。互相为援。而随敌所向。合力阻遏。则芦岭以北。亦可奠枕而作农矣。特令道臣按察形止。臣之所见如或不诬。从便施设。使其保障之所。得免废弃之地。则湖岭两路。俱得无忧矣。推此以往。东北两西。以及畿辅左右。或仍旧设。或加新筑。因势随便。皆有方略。如湖岭之为者。国中保障之所。星罗棋列。其势不期固而自固矣。议者必曰。虽有城池。军丁鲜少。保守之道为难。然若使列邑士民避乱者争趋。则其丽不亿。乡邑义师。随其所在。惟倚官军为重。何莫非战守之兵也。且我国男丁。多萃于僧徒。游衣游食。终归化外。其自列邑各寺。择才优者为僧将。而簿录年少之僧。作队教训。常时则别不劳忧。而及其有变。使之荷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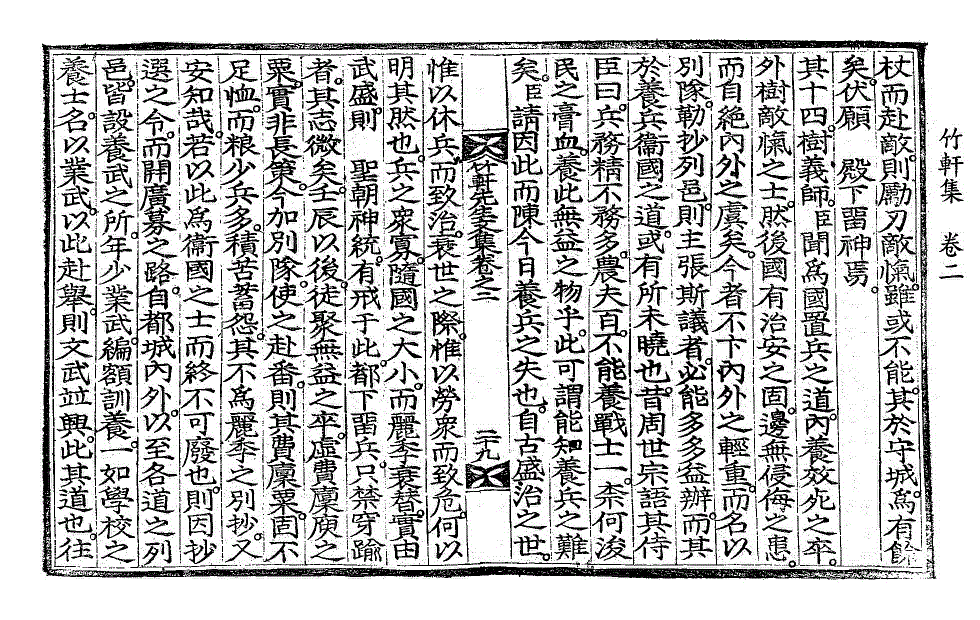 杖而赴敌。则励刃敌忾。虽或不能。其于守城。为有馀矣。伏愿 殿下留神焉。
杖而赴敌。则励刃敌忾。虽或不能。其于守城。为有馀矣。伏愿 殿下留神焉。[树义师]
其十四。树义师。臣闻为国置兵之道。内养效死之卒。外树敌忾之士。然后国有治安之固。边无侵侮之患。而自绝内外之虞矣。今者不卞内外之轻重。而名以别队。勒抄列邑。则主张斯议者。必能多多益办。而其于养兵卫国之道。或有所未晓也。昔周世宗语其侍臣曰。兵务精不务多。农夫百。不能养战士一。柰何浚民之膏血。养此无益之物乎。此可谓能知养兵之难矣。臣请因此而陈今日养兵之失也。自古盛治之世。惟以休兵而致治。衰世之际。惟以劳众而致危。何以明其然也。兵之众寡。随国之大小。而丽季衰替。实田武盛。则 圣朝神统。有戒于此。都下留兵。只禁穿踰者。其志微矣。壬辰以后。徒聚无益之卒。虚费廪庾之粟。实非长策。今加别队。使之赴番。则其费廪粟。固不足恤。而粮少兵多。积苦蓄怨。其不为丽季之别抄。又安知哉。若以此为卫国之士而终不可废也。则因抄选之令。而开广募之路。自都城内外。以至各道之列邑。皆设养武之所。年少业武。编额训养。一如学校之养士。名以业武。以此赴举。则文武并兴。此其道也。往
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2L 页
 古来今。扶颠拨乱。皆由于义士。名臣良将。多出于儒者。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于京乡。推儒品中才可堪者。名以义将。使之主管部署队伍。以定将卒。旬朔讲武。鍊习技艺。教之以出战入守之方。导之以亲上死长之义。且以道内秩高儒臣之有望者。别定位号而领之。春秋巡试。示以恩威。则将卒相倚。和信交孚。平居有定。临危不乱矣。自 朝廷时遣 御史而试才。拔其尤而直赴。序其次而施赏。使之兴起。勿使武将而临之。免其徵布之怨杂役之苦。则士夫之后裔。以及庶人之子弟。无文而有膂力者。皆归于此。别无抄选之劳。而咸有乐簿之心。不严搜括之令。而自无闲丁之漏。千万义士。一朝而募。不费廪粟而其养自裕。不烦鞭策。而其鍊自精。处常而为含恩之义师。遇变而为敌忾之猛士。列守四方。为国藩屏。内外轻重。俱得其宜。非但御㬥于南北。终为国家之倚重。 辇毂之下。虽无鍊卒。自无警急之患矣。且夫边海御倭之具。莫逾于车战。我国素无兵车之制。三道沿海。惟以战船为恃。倭船来迫之际。当锋合操。则犹或制贼。及其散归之时。贼出不意。则一二战船。决难独遏。倭船顺风。片时迫陆。无处不可。而三南诸镇。相距疏远。
古来今。扶颠拨乱。皆由于义士。名臣良将。多出于儒者。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于京乡。推儒品中才可堪者。名以义将。使之主管部署队伍。以定将卒。旬朔讲武。鍊习技艺。教之以出战入守之方。导之以亲上死长之义。且以道内秩高儒臣之有望者。别定位号而领之。春秋巡试。示以恩威。则将卒相倚。和信交孚。平居有定。临危不乱矣。自 朝廷时遣 御史而试才。拔其尤而直赴。序其次而施赏。使之兴起。勿使武将而临之。免其徵布之怨杂役之苦。则士夫之后裔。以及庶人之子弟。无文而有膂力者。皆归于此。别无抄选之劳。而咸有乐簿之心。不严搜括之令。而自无闲丁之漏。千万义士。一朝而募。不费廪粟而其养自裕。不烦鞭策。而其鍊自精。处常而为含恩之义师。遇变而为敌忾之猛士。列守四方。为国藩屏。内外轻重。俱得其宜。非但御㬥于南北。终为国家之倚重。 辇毂之下。虽无鍊卒。自无警急之患矣。且夫边海御倭之具。莫逾于车战。我国素无兵车之制。三道沿海。惟以战船为恃。倭船来迫之际。当锋合操。则犹或制贼。及其散归之时。贼出不意。则一二战船。决难独遏。倭船顺风。片时迫陆。无处不可。而三南诸镇。相距疏远。竹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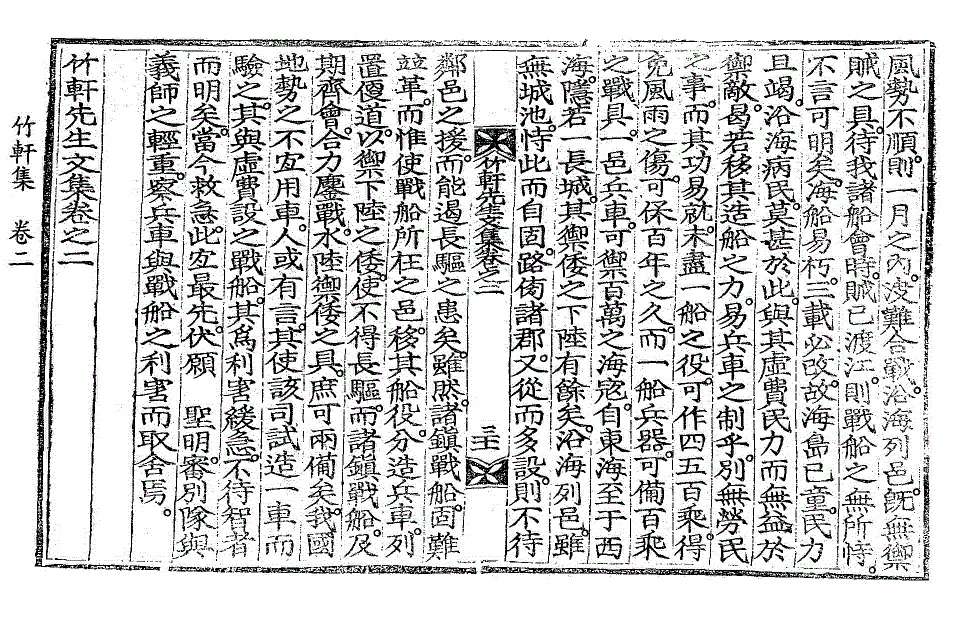 风势不顺。则一月之内。决难合战。沿海列邑。既无御贼之具。待我诸船会时。贼已渡江。则战船之无所恃。不言可明矣。海船易朽。三载必改。故海岛已童。民力且竭。沿海病民。莫甚于此。与其虚费民力而无益于御敌。曷若移其造船之力。易兵车之制乎。别无劳民之事。而其功易就。未尽一船之役。可作四五百乘。得免风雨之伤。可保百年之久。而一船兵器。可备百乘之战具。一邑兵车。可御百万之海寇。自东海至于西海。隐若一长城。其御倭之下陆有馀矣。沿海列邑。虽无城池。恃此而自固。路傍诸郡。又从而多设。则不待邻邑之援。而能遏长驱之患矣。虽然。诸镇战船。固难并革。而惟使战船所在之邑。移其船役。分造兵车。列置便道。以御下陆之倭。使不得长驱。而诸镇战船。及期齐会。合力鏖战。水陆御倭之具。庶可两备矣。我国地势之不宜用车。人或有言。其使该司试造一车而验之。其与虚费设之战船。其为利害缓急。不待智者而明矣。当今救急。此宜最先。伏愿 圣明。审别队与义师之轻重。察兵车与战船之利害而取舍焉。
风势不顺。则一月之内。决难合战。沿海列邑。既无御贼之具。待我诸船会时。贼已渡江。则战船之无所恃。不言可明矣。海船易朽。三载必改。故海岛已童。民力且竭。沿海病民。莫甚于此。与其虚费民力而无益于御敌。曷若移其造船之力。易兵车之制乎。别无劳民之事。而其功易就。未尽一船之役。可作四五百乘。得免风雨之伤。可保百年之久。而一船兵器。可备百乘之战具。一邑兵车。可御百万之海寇。自东海至于西海。隐若一长城。其御倭之下陆有馀矣。沿海列邑。虽无城池。恃此而自固。路傍诸郡。又从而多设。则不待邻邑之援。而能遏长驱之患矣。虽然。诸镇战船。固难并革。而惟使战船所在之邑。移其船役。分造兵车。列置便道。以御下陆之倭。使不得长驱。而诸镇战船。及期齐会。合力鏖战。水陆御倭之具。庶可两备矣。我国地势之不宜用车。人或有言。其使该司试造一车而验之。其与虚费设之战船。其为利害缓急。不待智者而明矣。当今救急。此宜最先。伏愿 圣明。审别队与义师之轻重。察兵车与战船之利害而取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