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经筵讲义]
[经筵讲义]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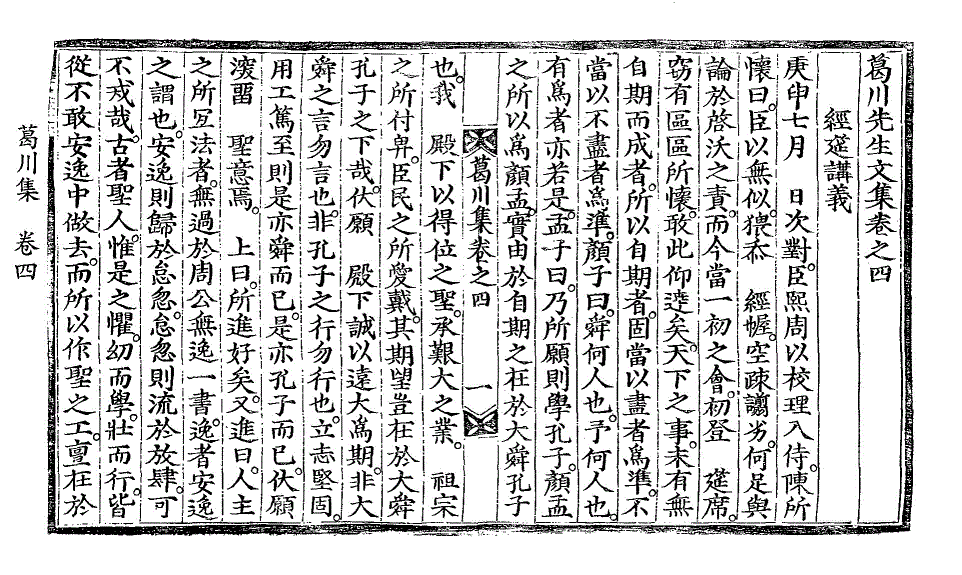 经筵讲义
经筵讲义庚申七月▣日次对。臣熙周以校理入侍。陈所怀曰。臣以无似。猥忝 经幄。空疏谫劣。何足与论于启沃之责。而今当一初之会。初登 筵席。窃有区区所怀。敢此仰达矣。天下之事。未有无自期而成者。所以自期者。固当以尽者为准。不当以不尽者为准。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颜孟之所以为颜孟。实由于自期之在于大舜孔子也。我 殿下以得位之圣。承艰大之业。 祖宗之所付畁。臣民之所爱戴。其期望岂在于大舜孔子之下哉。伏愿 殿下诚以远大为期。非大舜之言勿言也。非孔子之行勿行也。立志坚固。用工笃至则是亦舜而已。是亦孔子而已。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所进好矣。又进曰。人主之所宜法者。无过于周公无逸一书。逸者安逸之谓也。安逸则归于怠忽。怠忽则流于放肆。可不戒哉。古者圣人。惟是之惧。幼而学。壮而行。皆从不敢安逸中做去。而所以作圣之工。亶在于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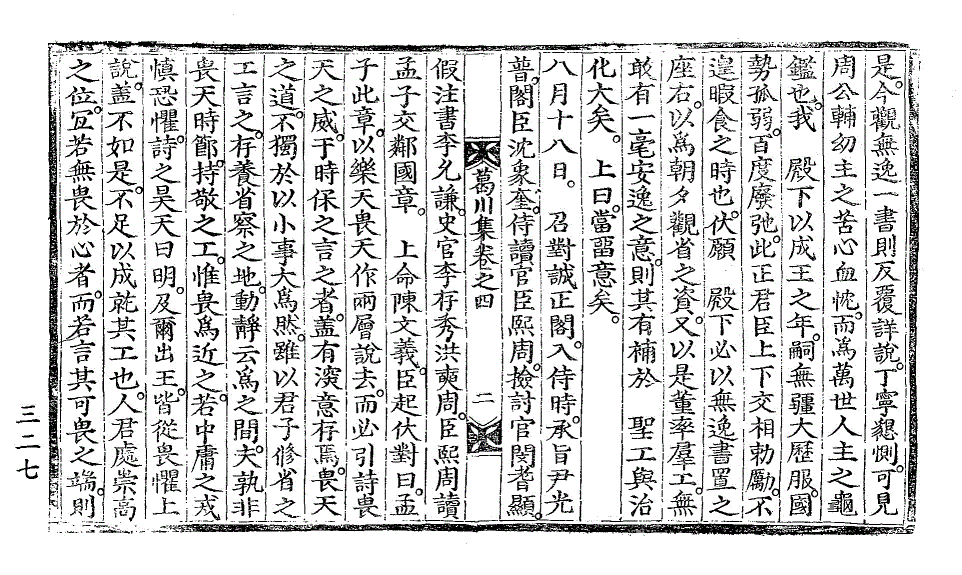 是。今观无逸一书则反覆详说。丁宁恳恻。可见周公辅幼主之苦心血忱。而为万世人主之龟鉴也。我 殿下以成王之年。嗣无疆大历服。国势孤弱。百度废弛。此正君臣上下交相敕励。不遑暇食之时也。伏愿 殿下必以无逸书置之座右。以为朝夕观省之资。又以是董率群工。无敢有一毫安逸之意。则其有补于 圣工与治化大矣。 上曰。当留意矣。
是。今观无逸一书则反覆详说。丁宁恳恻。可见周公辅幼主之苦心血忱。而为万世人主之龟鉴也。我 殿下以成王之年。嗣无疆大历服。国势孤弱。百度废弛。此正君臣上下交相敕励。不遑暇食之时也。伏愿 殿下必以无逸书置之座右。以为朝夕观省之资。又以是董率群工。无敢有一毫安逸之意。则其有补于 圣工与治化大矣。 上曰。当留意矣。八月十八日。 召对诚正阁。入侍时。承旨尹光普。阁臣沈象奎。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闵耆显。假注书李允谦。史官李存秀,洪奭周。臣熙周读孟子交邻国章。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孟子此章。以乐天畏天作两层说去。而必引诗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言之者。盖有深意存焉。畏天之道。不独于以小事大为然。虽以君子修省之工言之。存养省察之地。动静云为之间。夫孰非畏天时节。持敬之工。惟畏为近之。若中庸之戒慎恐惧。诗之昊天曰明。及尔出王。皆从畏惧上说。盖不如是。不足以成就其工也。人君处崇高之位。宜若无畏于心者。而若言其可畏之端。则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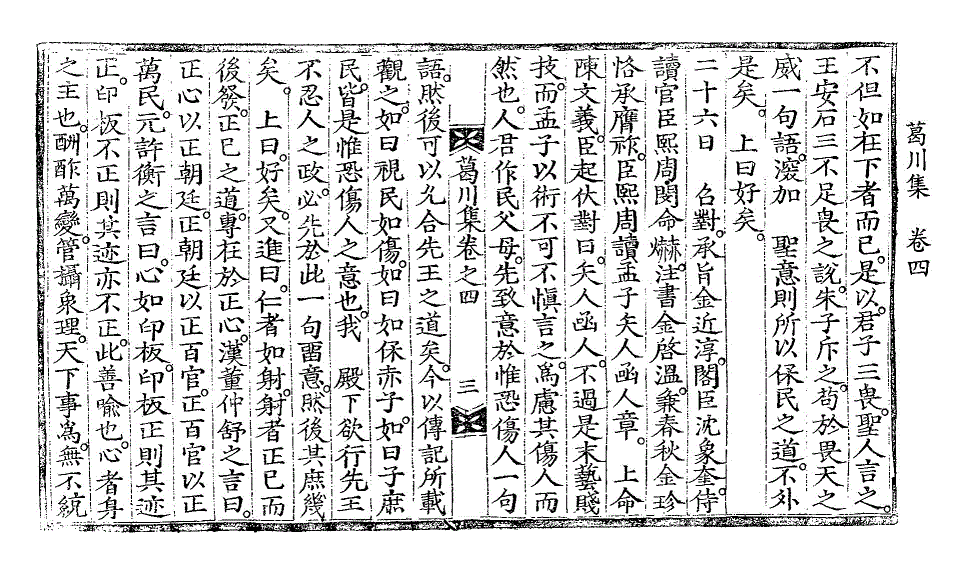 不但如在下者而已。是以。君子三畏。圣人言之。王安石三不足畏之说。朱子斥之。苟于畏天之威一句语。深加 圣意则所以保民之道。不外是矣。 上曰好矣。
不但如在下者而已。是以。君子三畏。圣人言之。王安石三不足畏之说。朱子斥之。苟于畏天之威一句语。深加 圣意则所以保民之道。不外是矣。 上曰好矣。二十六日 召对。承旨金近淳。阁臣沈象奎。侍读官臣熙周,闵命赫。注书金启温。兼春秋金珍恪承膺祚。臣熙周读孟子矢人函人章。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矢人函人。不过是末艺贱技。而孟子以术不可不慎言之。为虑其伤人而然也。人君作民父母。先致意于惟恐伤人一句语。然后可以允合先王之道矣。今以传记所载观之。如曰视民如伤。如曰如保赤子。如曰子庶民。皆是惟恐伤人之意也。我 殿下欲行先王不忍人之政。必先于此一句留意。然后其庶几矣。 上曰。好矣。又进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正己之道。专在于正心。汉董仲舒之言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元许衡之言曰。心如印板。印板正则其迹正。印板不正则其迹亦不正。此善喻也。心者身之主也。酬酢万变。管摄众理。天下事为。无不统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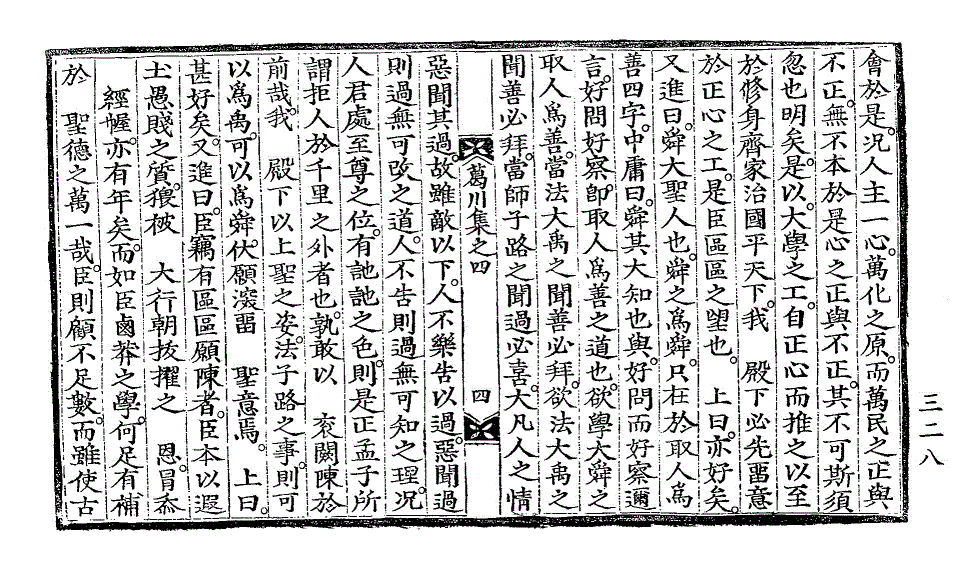 会于是。况人主一心。万化之原。而万民之正与不正。无不本于是心之正与不正。其不可斯须忽也明矣。是以。大学之工。自正心而推之以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 殿下必先留意于正心之工。是臣区区之望也。 上曰。亦好矣。又进曰。舜大圣人也。舜之为舜。只在于取人为善四字。中庸曰。舜其大知也与。好问而好察迩言。好问好察。即取人为善之道也。欲学大舜之取人为善。当法大禹之闻善必拜。欲法大禹之闻善必拜。当师子路之闻过必喜。大凡人之情恶闻其过。故虽敌以下。人不乐告以过。恶闻过则过无可改之道。人不告则过无可知之理。况人君处至尊之位。有訑訑之色。则是正孟子所谓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也。孰敢以 衮阙陈于前哉。我 殿下以上圣之姿。法子路之事。则可以为禹。可以为舜。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甚好矣。又进曰。臣窃有区区愿陈者。臣本以遐土愚贱之质。猥被 大行朝拔擢之 恩。冒忝 经幄。亦有年矣。而如臣卤莽之学。何足有补于 圣德之万一哉。臣则顾不足数。而虽使古
会于是。况人主一心。万化之原。而万民之正与不正。无不本于是心之正与不正。其不可斯须忽也明矣。是以。大学之工。自正心而推之以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 殿下必先留意于正心之工。是臣区区之望也。 上曰。亦好矣。又进曰。舜大圣人也。舜之为舜。只在于取人为善四字。中庸曰。舜其大知也与。好问而好察迩言。好问好察。即取人为善之道也。欲学大舜之取人为善。当法大禹之闻善必拜。欲法大禹之闻善必拜。当师子路之闻过必喜。大凡人之情恶闻其过。故虽敌以下。人不乐告以过。恶闻过则过无可改之道。人不告则过无可知之理。况人君处至尊之位。有訑訑之色。则是正孟子所谓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也。孰敢以 衮阙陈于前哉。我 殿下以上圣之姿。法子路之事。则可以为禹。可以为舜。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甚好矣。又进曰。臣窃有区区愿陈者。臣本以遐土愚贱之质。猥被 大行朝拔擢之 恩。冒忝 经幄。亦有年矣。而如臣卤莽之学。何足有补于 圣德之万一哉。臣则顾不足数。而虽使古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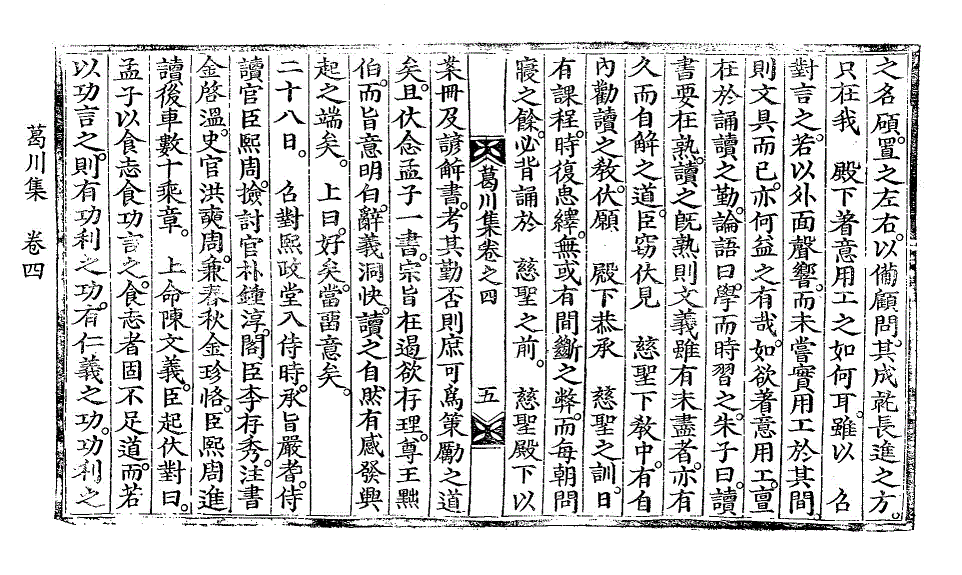 之名硕。置之左右。以备顾问。其成就长进之方。只在我 殿下着意用工之如何耳。虽以 召对言之。若以外面声响。而未尝实用工于其间。则文具而已。亦何益之有哉。如欲着意用工。亶在于诵读之勤。论语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曰。读书要在熟。读之既熟则文义虽有未尽者。亦有久而自解之道。臣窃伏见 慈圣下教中。有自内劝读之教。伏愿 殿下恭承 慈圣之训。日有课程。时复思绎。无或有间断之弊。而每朝问寝之馀。必背诵于 慈圣之前。 慈圣殿下以案册及谚解书。考其勤否则庶可为策励之道矣。且伏念孟子一书。宗旨在遏欲存理。尊王黜伯。而旨意明白。辞义洞快。读之自然有感发兴起之端矣。 上曰。好矣。当留意矣。
之名硕。置之左右。以备顾问。其成就长进之方。只在我 殿下着意用工之如何耳。虽以 召对言之。若以外面声响。而未尝实用工于其间。则文具而已。亦何益之有哉。如欲着意用工。亶在于诵读之勤。论语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曰。读书要在熟。读之既熟则文义虽有未尽者。亦有久而自解之道。臣窃伏见 慈圣下教中。有自内劝读之教。伏愿 殿下恭承 慈圣之训。日有课程。时复思绎。无或有间断之弊。而每朝问寝之馀。必背诵于 慈圣之前。 慈圣殿下以案册及谚解书。考其勤否则庶可为策励之道矣。且伏念孟子一书。宗旨在遏欲存理。尊王黜伯。而旨意明白。辞义洞快。读之自然有感发兴起之端矣。 上曰。好矣。当留意矣。二十八日。 召对熙政堂入侍时。承旨严耆。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朴钟淳。阁臣李存秀。注书金启温。史官洪奭周。兼春秋金珍恪。臣熙周进读后车数十乘章。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孟子以食志食功言之。食志者固不足道。而若以功言之。则有功利之功。有仁义之功。功利之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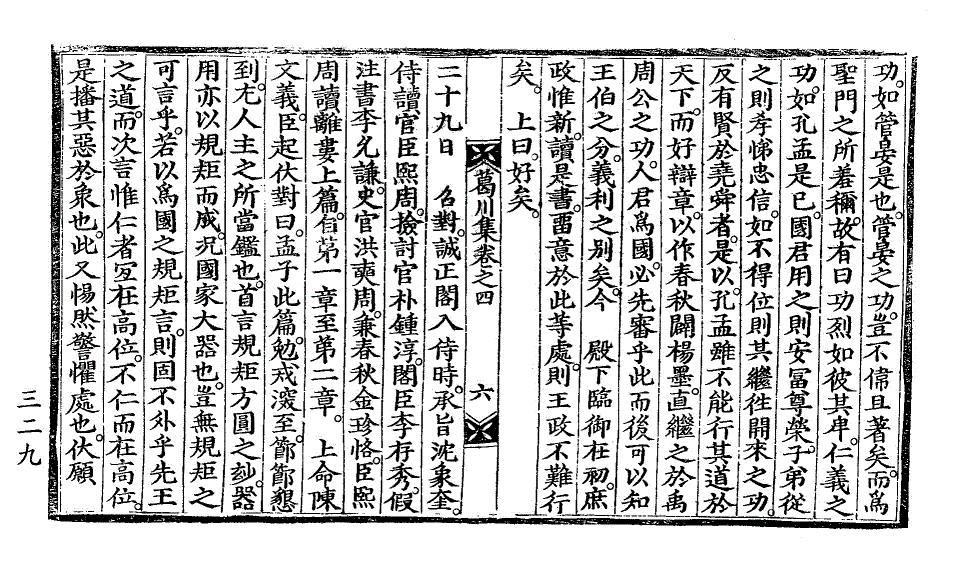 功。如管,晏是也。管,晏之功。岂不伟且著矣。而为圣门之所羞称。故有曰功烈如彼其卑。仁义之功。如孔孟是已。国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如不得位则其继往开来之功。反有贤于尧舜者。是以。孔孟虽不能行其道于天下。而好辩章。以作春秋辟杨墨。直继之于禹周公之功。人君为国。必先审乎此而后可以知王伯之分。义利之别矣。今 殿下临御在初。庶政惟新。读是书。留意于此等处。则王政不难行矣。 上曰。好矣。
功。如管,晏是也。管,晏之功。岂不伟且著矣。而为圣门之所羞称。故有曰功烈如彼其卑。仁义之功。如孔孟是已。国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如不得位则其继往开来之功。反有贤于尧舜者。是以。孔孟虽不能行其道于天下。而好辩章。以作春秋辟杨墨。直继之于禹周公之功。人君为国。必先审乎此而后可以知王伯之分。义利之别矣。今 殿下临御在初。庶政惟新。读是书。留意于此等处。则王政不难行矣。 上曰。好矣。二十九日 召对。诚正阁入侍时。承旨沈象奎。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朴钟淳。阁臣李存秀。假注书李允谦。史官洪奭周。兼春秋金珍恪。臣熙周读离娄上篇。自第一章至第二章。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孟子此篇。勉戒深至。节节恳到。尤人主之所当鉴也。首言规矩方圆之妙。器用亦以规矩而成。况国家大器也。岂无规矩之可言乎。若以为国之规矩言。则固不外乎先王之道。而次言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此又惕然警惧处也。伏愿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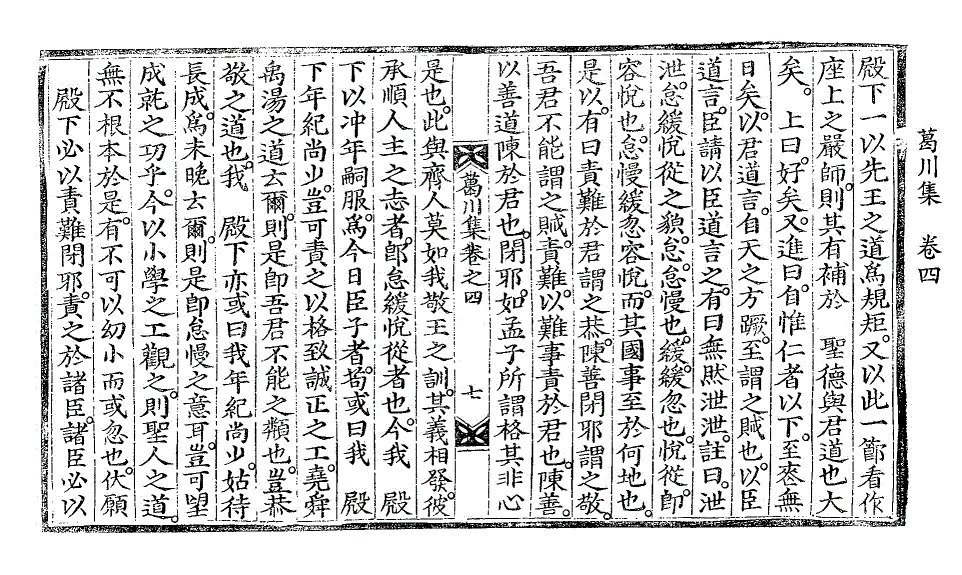 殿下一以先王之道为规矩。又以此一节看作座上之严师。则其有补于 圣德与君道也大矣。 上曰。好矣。又进曰。自惟仁者以下。至丧无日矣。以君道言。自天之方蹶。至谓之贼也。以臣道言。臣请以臣道言之。有曰无然泄泄。注曰。泄泄。怠缓悦从之貌。怠。怠慢也。缓。缓忽也。悦从。即容悦也。怠慢缓忽容悦。而其国事至于何地也。是以。有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责难。以难事责于君也。陈善。以善道陈于君也。闭邪。如孟子所谓格其非心是也。此与齐人莫如我敬王之训。其义相发。彼承顺人主之志者。即怠缓悦从者也。今我 殿下以冲年嗣服。为今日臣子者。苟或曰我 殿下年纪尚少。岂可责之以格致诚正之工。尧舜禹汤之道云尔。则是即吾君不能之类也。岂恭敬之道也。我 殿下亦或曰我年纪尚少。姑待长成。为未晚云尔。则是即怠慢之意耳。岂可望成就之功乎。今以小学之工观之。则圣人之道。无不根本于是。有不可以幼小而或忽也。伏愿 殿下必以责难闭邪。责之于诸臣。诸臣必以
殿下一以先王之道为规矩。又以此一节看作座上之严师。则其有补于 圣德与君道也大矣。 上曰。好矣。又进曰。自惟仁者以下。至丧无日矣。以君道言。自天之方蹶。至谓之贼也。以臣道言。臣请以臣道言之。有曰无然泄泄。注曰。泄泄。怠缓悦从之貌。怠。怠慢也。缓。缓忽也。悦从。即容悦也。怠慢缓忽容悦。而其国事至于何地也。是以。有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责难。以难事责于君也。陈善。以善道陈于君也。闭邪。如孟子所谓格其非心是也。此与齐人莫如我敬王之训。其义相发。彼承顺人主之志者。即怠缓悦从者也。今我 殿下以冲年嗣服。为今日臣子者。苟或曰我 殿下年纪尚少。岂可责之以格致诚正之工。尧舜禹汤之道云尔。则是即吾君不能之类也。岂恭敬之道也。我 殿下亦或曰我年纪尚少。姑待长成。为未晚云尔。则是即怠慢之意耳。岂可望成就之功乎。今以小学之工观之。则圣人之道。无不根本于是。有不可以幼小而或忽也。伏愿 殿下必以责难闭邪。责之于诸臣。诸臣必以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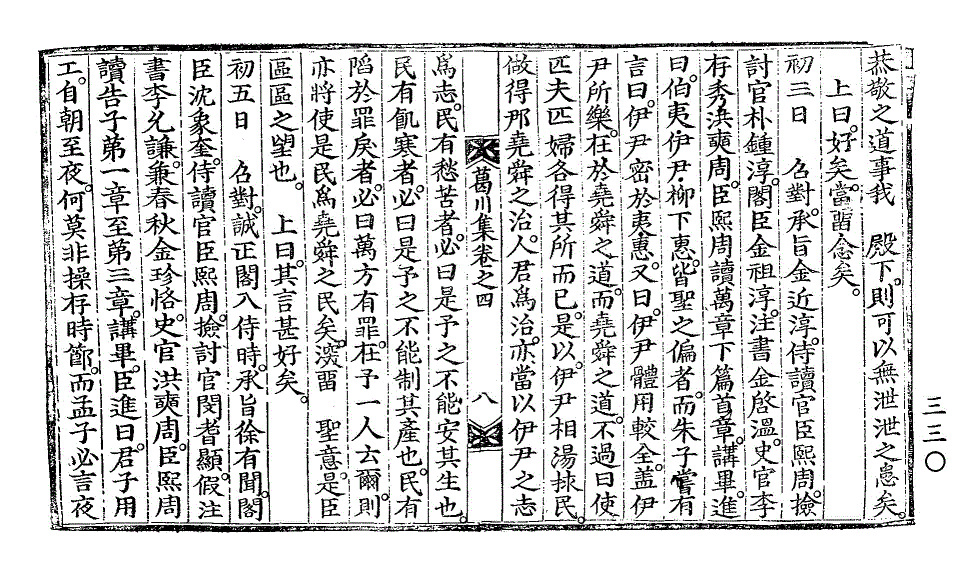 恭敬之道事我 殿下。则可以无泄泄之患矣。 上曰。好矣。当留念矣。
恭敬之道事我 殿下。则可以无泄泄之患矣。 上曰。好矣。当留念矣。初三日 召对。承旨金近淳。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朴钟淳。阁臣金祖淳。注书金启温。史官李存秀,洪奭周。臣熙周读万章下篇首章。讲毕。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圣之偏者。而朱子尝有言曰。伊尹密于夷,惠。又曰。伊尹体用较全。盖伊尹所乐。在于尧舜之道。而尧舜之道。不过曰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而已。是以。伊尹相汤救民。做得那尧舜之治。人君为治。亦当以伊尹之志为志。民有愁苦者。必曰是予之不能安其生也。民有饥寒者。必曰是予之不能制其产也。民有陷于罪戾者。必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云尔。则亦将使是民为尧舜之民矣。深留 圣意。是臣区区之望也。 上曰。其言甚好矣。
初五日 召对。诚正阁入侍时。承旨徐有闻。阁臣沈象奎。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闵耆显。假注书李允谦。兼春秋金珍恪。史官洪奭周。臣熙周读告子第一章至第三章。讲毕。臣进曰。君子用工。自朝至夜。何莫非操存时节。而孟子必言夜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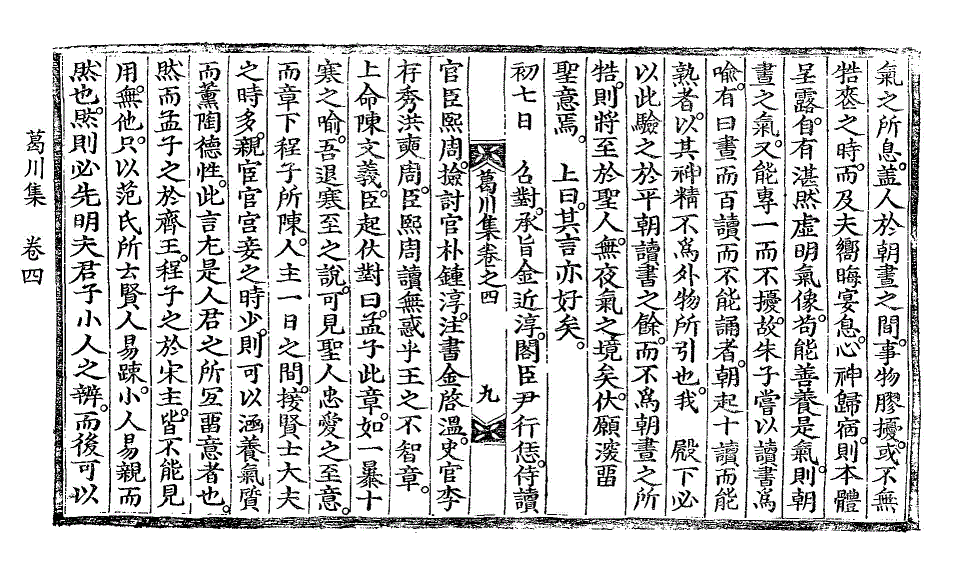 气之所息。盖人于朝昼之间。事物胶扰。或不无牿丧之时。而及夫向晦宴息。心神归宿。则本体呈露。自有湛然虚明气像。苟能善养是气。则朝昼之气。又能专一而不扰。故朱子尝以读书为喻。有曰昼而百读而不能诵者。朝起十读而能熟者。以其神精不为外物所引也。我 殿下必以此验之于平朝读书之馀。而不为朝昼之所牿。则将至于圣人。无夜气之境矣。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其言亦好矣。
气之所息。盖人于朝昼之间。事物胶扰。或不无牿丧之时。而及夫向晦宴息。心神归宿。则本体呈露。自有湛然虚明气像。苟能善养是气。则朝昼之气。又能专一而不扰。故朱子尝以读书为喻。有曰昼而百读而不能诵者。朝起十读而能熟者。以其神精不为外物所引也。我 殿下必以此验之于平朝读书之馀。而不为朝昼之所牿。则将至于圣人。无夜气之境矣。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其言亦好矣。初七日 召对。承旨金近淳。阁臣尹行恁。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朴钟淳。注书金启温。史官李存秀,洪奭周。臣熙周读无惑乎王之不智章。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孟子此章。如一㬥十寒之喻。吾退寒至之说。可见圣人忠爱之至意。而章下程子所陈。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可以涵养气质而薰陶德性。此言尤是人君之所宜留意者也。然而孟子之于齐王。程子之于宋主。皆不能见用。无他。只以范氏所云贤人易疏。小人易亲而然也。然则必先明夫君子小人之辨。而后可以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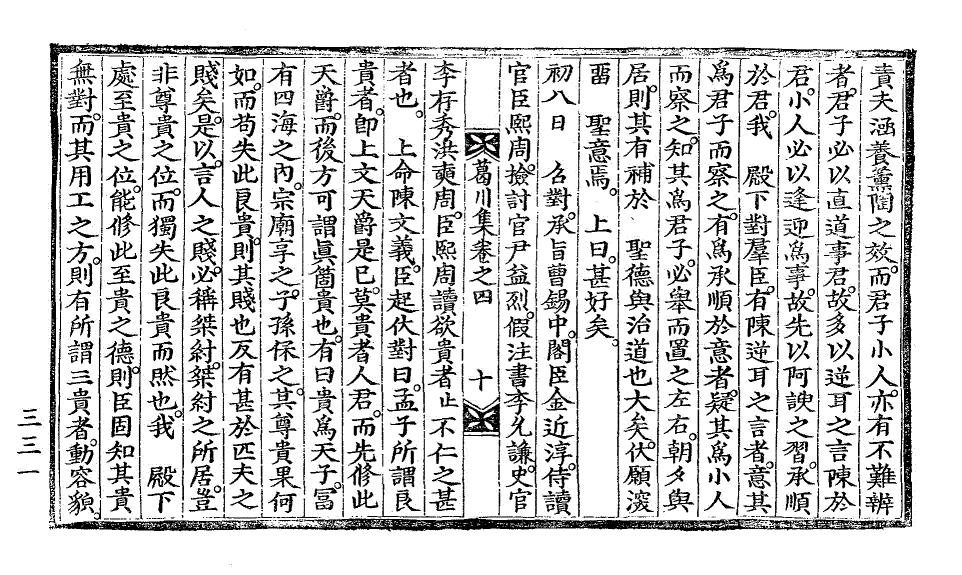 责夫涵养薰陶之效。而君子小人。亦有不难辨者。君子必以直道事君。故多以逆耳之言陈于君。小人必以逢迎为事。故先以阿谀之习。承顺于君。我 殿下对群臣。有陈逆耳之言者。意其为君子而察之。有为承顺于意者。疑其为小人而察之。知其为君子。必举而置之左右。朝夕与居。则其有补于 圣德与治道也大矣。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甚好矣。
责夫涵养薰陶之效。而君子小人。亦有不难辨者。君子必以直道事君。故多以逆耳之言陈于君。小人必以逢迎为事。故先以阿谀之习。承顺于君。我 殿下对群臣。有陈逆耳之言者。意其为君子而察之。有为承顺于意者。疑其为小人而察之。知其为君子。必举而置之左右。朝夕与居。则其有补于 圣德与治道也大矣。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甚好矣。初八日 召对。承旨曹锡中。阁臣金近淳。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尹益烈。假注书李允谦。史官李存秀,洪奭周。臣熙周读欲贵者(止)不仁之甚者也。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孟子所谓良贵者。即上文天爵是已。莫贵者人君。而先修此天爵。而后方可谓真个贵也。有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其尊贵果何如。而苟失此良贵。则其贱也反有甚于匹夫之贱矣。是以。言人之贱。必称桀纣。桀纣之所居。岂非尊贵之位。而独失此良贵而然也。我 殿下处至贵之位。能修此至贵之德。则臣固知其贵无对。而其用工之方。则有所谓三贵者。动容貌。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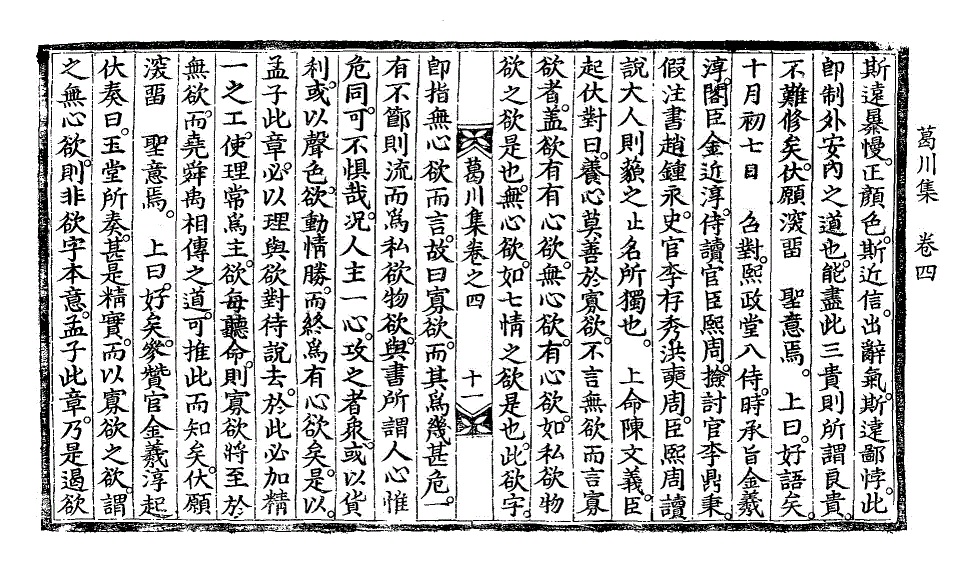 斯远㬥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悖。此即制外安内之道也。能尽此三贵则所谓良贵。不难修矣。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好语矣。
斯远㬥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悖。此即制外安内之道也。能尽此三贵则所谓良贵。不难修矣。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好语矣。十月初七日 召对。熙政堂入侍。时承旨金羲淳。阁臣金近淳。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李鼎秉。假注书赵钟永。史官李存秀,洪奭周。臣熙周读说大人则藐之(止)名所独也。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不言无欲而言寡欲者。盖欲有有心欲。无心欲。有心欲。如私欲物欲之欲是也。无心欲。如七情之欲是也。此欲字。即指无心欲而言。故曰寡欲。而其为几甚危。一有不节则流而为私欲物欲。与书所谓人心惟危同。可不惧哉。况人主一心。攻之者众。或以货利。或以声色。欲动情胜。而终为有心欲矣。是以。孟子此章。必以理与欲对待说去。于此必加精一之工。使理常为主。欲每听命。则寡欲将至于无欲。而尧舜禹相传之道。可推此而知矣。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好矣。参赞官金羲淳起伏奏曰。玉堂所奏。甚是精实。而以寡欲之欲。谓之无心欲。则非欲字本意。孟子此章。乃是遏欲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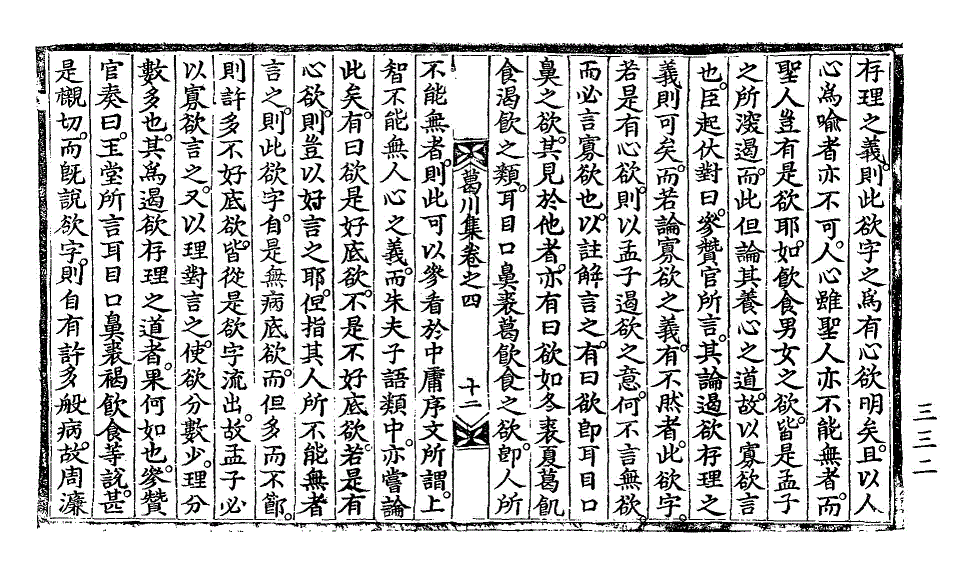 存理之义。则此欲字之为有心欲明矣。且以人心为喻者亦不可。人心虽圣人亦不能无者。而圣人岂有是欲耶。如饮食男女之欲。皆是孟子之所深遏。而此但论其养心之道。故以寡欲言也。臣起伏对曰。参赞官所言。其论遏欲存理之义则可矣。而若论寡欲之义。有不然者。此欲字。若是有心欲。则以孟子遏欲之意。何不言无欲。而必言寡欲也。以注解言之。有曰欲即耳目口鼻之欲。其见于他者。亦有曰欲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之类。耳目口鼻裘葛饮食之欲。即人所不能无者。则此可以参看于中庸序文所谓。上智不能无人心之义。而朱夫子语类中。亦尝论此矣。有曰欲是好底欲。不是不好底欲。若是有心欲。则岂以好言之耶。但指其人所不能无者言之。则此欲字。自是无病底欲。而但多而不节。则许多不好底欲。皆从是欲字流出。故孟子必以寡欲言之。又以理对言之。使欲分数少。理分数多也。其为遏欲存理之道者。果何如也。参赞官奏曰。玉堂所言耳目口鼻裘褐饮食等说。甚是衬切。而既说欲字。则自有许多般病。故周濂
存理之义。则此欲字之为有心欲明矣。且以人心为喻者亦不可。人心虽圣人亦不能无者。而圣人岂有是欲耶。如饮食男女之欲。皆是孟子之所深遏。而此但论其养心之道。故以寡欲言也。臣起伏对曰。参赞官所言。其论遏欲存理之义则可矣。而若论寡欲之义。有不然者。此欲字。若是有心欲。则以孟子遏欲之意。何不言无欲。而必言寡欲也。以注解言之。有曰欲即耳目口鼻之欲。其见于他者。亦有曰欲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之类。耳目口鼻裘葛饮食之欲。即人所不能无者。则此可以参看于中庸序文所谓。上智不能无人心之义。而朱夫子语类中。亦尝论此矣。有曰欲是好底欲。不是不好底欲。若是有心欲。则岂以好言之耶。但指其人所不能无者言之。则此欲字。自是无病底欲。而但多而不节。则许多不好底欲。皆从是欲字流出。故孟子必以寡欲言之。又以理对言之。使欲分数少。理分数多也。其为遏欲存理之道者。果何如也。参赞官奏曰。玉堂所言耳目口鼻裘褐饮食等说。甚是衬切。而既说欲字。则自有许多般病。故周濂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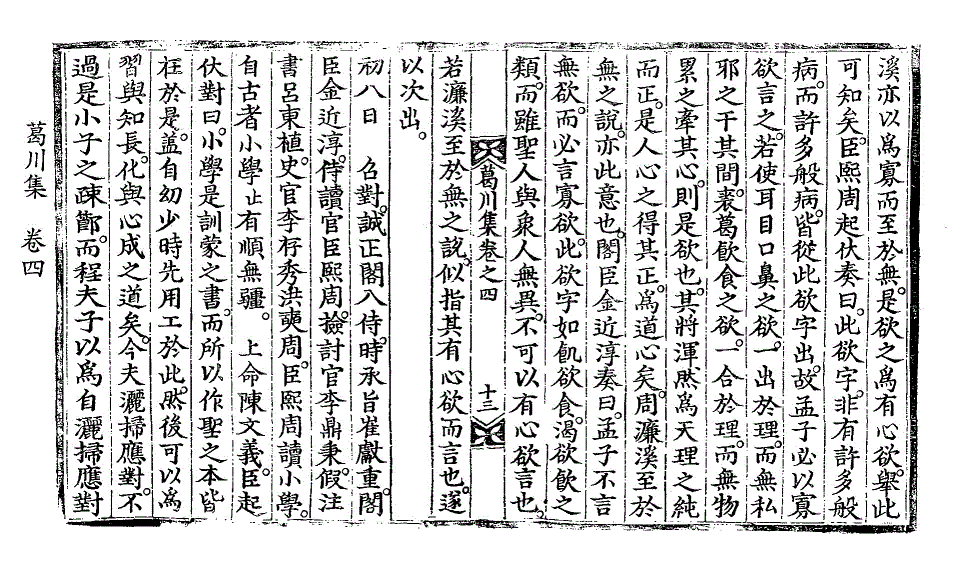 溪亦以为寡而至于无。是欲之为有心欲。举此可知矣。臣熙周起伏奏曰。此欲字。非有许多般病。而许多般病。皆从此欲字出。故孟子必以寡欲言之。若使耳目口鼻之欲。一出于理。而无私邪之干其间。裘葛饮食之欲。一合于理。而无物累之牵其心。则是欲也。其将浑然为天理之纯而正。是人心之得其正。为道心矣。周濂溪至于无之说。亦此意也。阁臣金近淳奏曰。孟子不言无欲。而必言寡欲。此欲字如饥欲食。渴欲饮之类。而虽圣人与众人无异。不可以有心欲言也。若濂溪至于无之说。似指其有心欲而言也。遂以次出。
溪亦以为寡而至于无。是欲之为有心欲。举此可知矣。臣熙周起伏奏曰。此欲字。非有许多般病。而许多般病。皆从此欲字出。故孟子必以寡欲言之。若使耳目口鼻之欲。一出于理。而无私邪之干其间。裘葛饮食之欲。一合于理。而无物累之牵其心。则是欲也。其将浑然为天理之纯而正。是人心之得其正。为道心矣。周濂溪至于无之说。亦此意也。阁臣金近淳奏曰。孟子不言无欲。而必言寡欲。此欲字如饥欲食。渴欲饮之类。而虽圣人与众人无异。不可以有心欲言也。若濂溪至于无之说。似指其有心欲而言也。遂以次出。初八日 召对。诚正阁入侍。时承旨崔献重。阁臣金近淳。侍读官臣熙周。捡讨官李鼎秉。假注书吕东植。史官李存秀,洪奭周。臣熙周读小学。自古者小学(止)有顺无疆。 上命陈文义。臣起伏对曰。小学是训蒙之书。而所以作圣之本皆在于是。盖自幼少时先用工于此。然后可以为习与知长。化与心成之道矣。今夫洒扫应对。不过是小子之疏节。而程夫子以为自洒扫应对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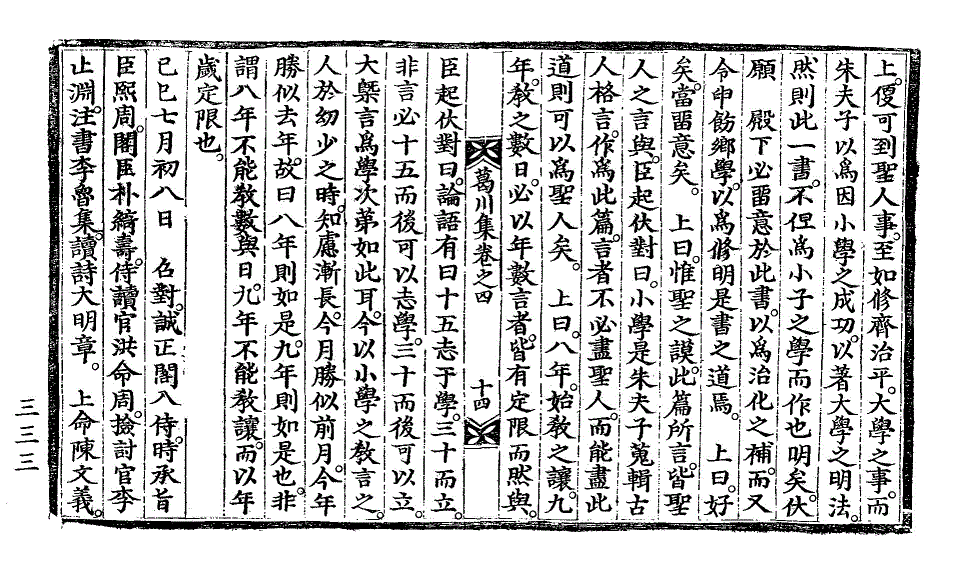 上。便可到圣人事。至如修齐治平。大学之事。而朱夫子以为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然则此一书。不但为小子之学而作也明矣。伏愿 殿下必留意于此书。以为治化之补。而又令申饬乡学。以为修明是书之道焉。 上曰。好矣。当留意矣。 上曰。惟圣之谟。此篇所言。皆圣人之言与。臣起伏对曰。小学是朱夫子蒐辑古人格言。作为此篇。言者不必尽圣人。而能尽此道则可以为圣人矣。 上曰。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必以年数言者。皆有定限而然与。臣起伏对曰。论语有曰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非言必十五而后可以志学。三十而后可以立。大槩言为学次第如此耳。今以小学之教言之。人于幼少之时。知虑渐长。今月胜似前月。今年胜似去年。故曰八年则如是。九年则如是也。非谓八年不能教数与日。九年不能教让。而以年岁定限也。
上。便可到圣人事。至如修齐治平。大学之事。而朱夫子以为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然则此一书。不但为小子之学而作也明矣。伏愿 殿下必留意于此书。以为治化之补。而又令申饬乡学。以为修明是书之道焉。 上曰。好矣。当留意矣。 上曰。惟圣之谟。此篇所言。皆圣人之言与。臣起伏对曰。小学是朱夫子蒐辑古人格言。作为此篇。言者不必尽圣人。而能尽此道则可以为圣人矣。 上曰。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必以年数言者。皆有定限而然与。臣起伏对曰。论语有曰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非言必十五而后可以志学。三十而后可以立。大槩言为学次第如此耳。今以小学之教言之。人于幼少之时。知虑渐长。今月胜似前月。今年胜似去年。故曰八年则如是。九年则如是也。非谓八年不能教数与日。九年不能教让。而以年岁定限也。己巳七月初八日 召对。诚正阁入侍。时承旨臣熙周。阁臣朴绮寿。侍读官洪命周。捡讨官李止渊。注书李鲁集。读诗大明章。 上命陈文义。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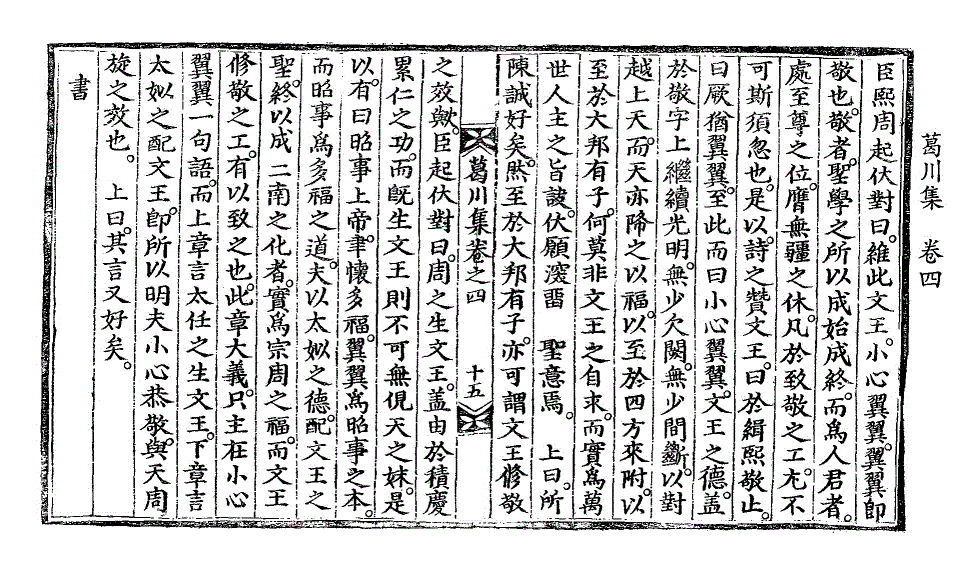 臣熙周起伏对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即敬也。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而为人君者。处至尊之位。膺无疆之休。凡于致敬之工。尤不可斯须忽也。是以。诗之赞文王。曰于缉熙敬止。曰厥犹翼翼。至此而曰小心翼翼。文王之德。盖于敬字上继续光明。无少欠阙。无少间断。以对越上天。而天亦降之以福。以至于四方来附。以至于大邦有子。何莫非文王之自求。而实为万世人主之旨诀。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所陈诚好矣。然至于大邦有子。亦可谓文王修敬之效欤。臣起伏对曰。周之生文王。盖由于积庆累仁之功。而既生文王则不可无伣天之妹。是以。有曰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翼翼为昭事之本。而昭事为多福之道。夫以太姒之德。配文王之圣。终以成二南之化者。实为宗周之福。而文王修敬之工。有以致之也。此章大义。只主在小心翼翼一句语。而上章言太任之生文王。下章言太姒之配文王。即所以明夫小心恭敬。与天周旋之效也。 上曰。其言又好矣。
臣熙周起伏对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即敬也。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而为人君者。处至尊之位。膺无疆之休。凡于致敬之工。尤不可斯须忽也。是以。诗之赞文王。曰于缉熙敬止。曰厥犹翼翼。至此而曰小心翼翼。文王之德。盖于敬字上继续光明。无少欠阙。无少间断。以对越上天。而天亦降之以福。以至于四方来附。以至于大邦有子。何莫非文王之自求。而实为万世人主之旨诀。伏愿深留 圣意焉。 上曰。所陈诚好矣。然至于大邦有子。亦可谓文王修敬之效欤。臣起伏对曰。周之生文王。盖由于积庆累仁之功。而既生文王则不可无伣天之妹。是以。有曰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翼翼为昭事之本。而昭事为多福之道。夫以太姒之德。配文王之圣。终以成二南之化者。实为宗周之福。而文王修敬之工。有以致之也。此章大义。只主在小心翼翼一句语。而上章言太任之生文王。下章言太姒之配文王。即所以明夫小心恭敬。与天周旋之效也。 上曰。其言又好矣。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书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4L 页
 上韩相国(用龟○丙子)
上韩相国(用龟○丙子)伏惟日间。匀体气候一向万安。每念疏贱之踪。得一进拜。必开颜接辞。倾倒无馀。自顾无似。何以得此于大人君子也。感荷之极。无以为喻。先师大山先生褒 赠事。前已拜教。而向来宰臣疏。自是公共之议。非出阿好之私。盖其造诣浅深。今不必更事覼缕。而其为数百年来南士之大宗师。则岭之妇孺皆知之矣。自 朝家特施优异之典。实为扶世教卫斯道之大关。未知如何。我朝于道学节义。所以揄扬之褒赠之。每出常格之外。如郑一蠹,徐花潭。皆以微品直 赠崇秩。此其已事之可验。而儒贤表著者。虽非正二品。特许赐谥。已载大典中矣。方今朝野之望。专系于閤下。禀处之责。又在于閤下。若失此时。九重深远。不知何时可以准请。幸须更加商量。特以崇秩美谥 启请。副多士之望。千万。
答尹侯(鲁东○丁丑)
伏承下书。谨审秋凉。字抚动止万安。区区仰慰。乡饮酒礼。今之人得见古道。何等喜幸。仪节。自仪礼以后代各异制。而节目比古稍减者。必以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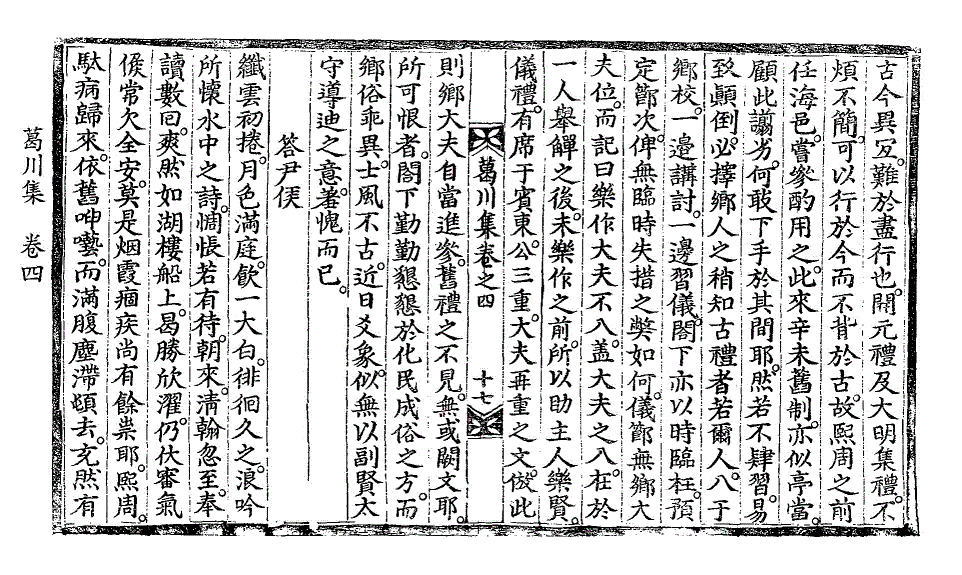 古今异宜。难于尽行也。开元礼及大明集礼。不烦不简。可以行于今而不背于古。故熙周之前任海邑。尝参酌用之。此来辛未旧制。亦似亭当。顾此谫劣。何敢下手于其间耶。然若不肄习。易致颠倒。必择乡人之稍知古礼者若尔人。入于乡校。一边讲讨。一边习仪。閤下亦以时临枉。预定节次。俾无临时失措之弊如何。仪节无乡大夫位。而记曰乐作大夫不入。盖大夫之入。在于一人举觯之后。未乐作之前。所以助主人乐贤。仪礼。有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之文。仿此则乡大夫自当进参。旧礼之不见。无或阙文耶。所可恨者。閤下勤勤恳恳于化民成俗之方。而乡俗乖异。士风不古。近日爻象。似无以副贤太守导迪之意。羞愧而已。
古今异宜。难于尽行也。开元礼及大明集礼。不烦不简。可以行于今而不背于古。故熙周之前任海邑。尝参酌用之。此来辛未旧制。亦似亭当。顾此谫劣。何敢下手于其间耶。然若不肄习。易致颠倒。必择乡人之稍知古礼者若尔人。入于乡校。一边讲讨。一边习仪。閤下亦以时临枉。预定节次。俾无临时失措之弊如何。仪节无乡大夫位。而记曰乐作大夫不入。盖大夫之入。在于一人举觯之后。未乐作之前。所以助主人乐贤。仪礼。有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之文。仿此则乡大夫自当进参。旧礼之不见。无或阙文耶。所可恨者。閤下勤勤恳恳于化民成俗之方。而乡俗乖异。士风不古。近日爻象。似无以副贤太守导迪之意。羞愧而已。答尹侯
纤云初捲。月色满庭。饮一大白。徘徊久之。浪吟所怀水中之诗。惆怅若有待。朝来。清翰忽至。奉读数回。爽然如湖楼船上。曷胜欣濯。仍伏审气候常欠全安。莫是烟霞痼疾尚有馀祟耶。熙周。驮病归来。依旧呻呓。而满腹尘滞顿去。充然有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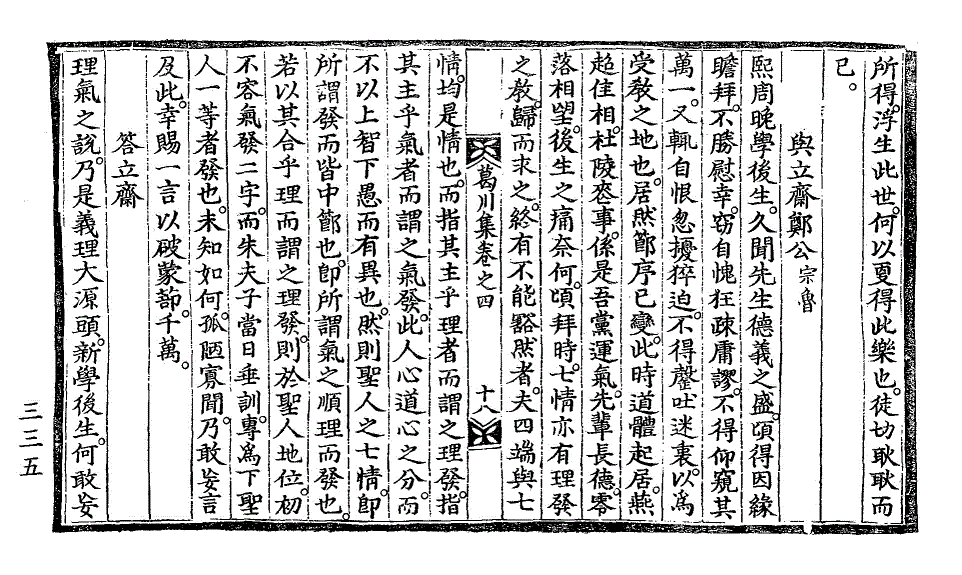 所得。浮生此世。何以更得此乐也。徒切耿耿而已。
所得。浮生此世。何以更得此乐也。徒切耿耿而已。与立斋郑公(宗鲁)
熙周晚学后生。久闻先生德义之盛。顷得因缘瞻拜。不胜慰幸。窃自愧狂疏庸谬。不得仰窥其万一。又辄自恨匆扰猝迫。不得罄吐迷衷。以为受教之地也。居然节序已变。此时道体起居。燕超佳相。杜陵丧事。系是吾党运气。先辈长德。零落相望。后生之痛奈何。顷拜时。七情亦有理发之教。归而求之。终有不能豁然者。夫四端与七情。均是情也。而指其主乎理者而谓之理发。指其主乎气者而谓之气发。此人心道心之分。而不以上智下愚而有异也。然则圣人之七情。即所谓发而皆中节也。即所谓气之顺理而发也。若以其合乎理而谓之理发。则于圣人地位。初不容气发二字。而朱夫子当日垂训。专为下圣人一等者发也。未知如何。孤陋寡闻。乃敢妄言及此。幸赐一言以破蒙蔀。千万。
答立斋
理气之说。乃是义理大源头。新学后生。何敢妄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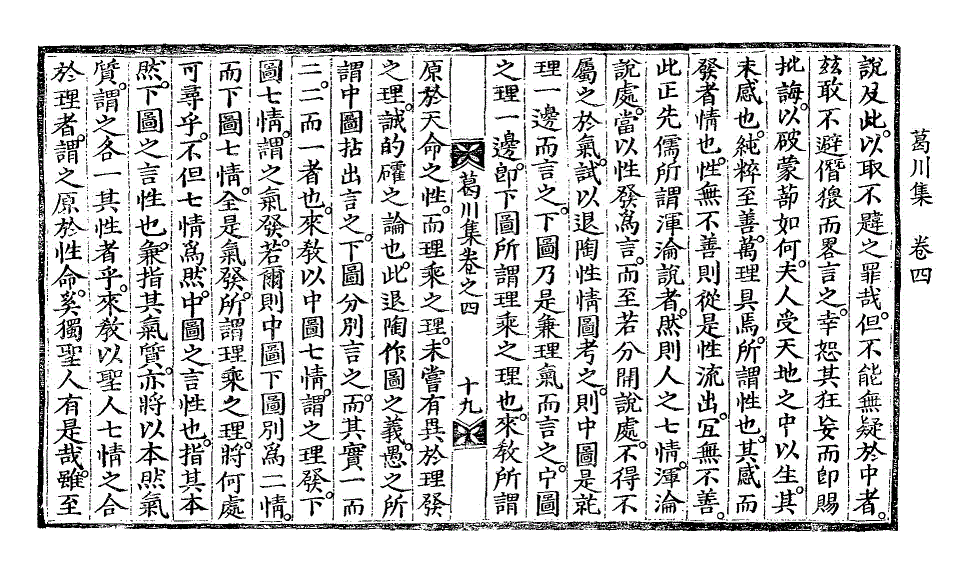 说及此。以取不韪之罪哉。但不能无疑于中者。玆敢不避僭猥而略言之。幸恕其狂妄而即赐批诲。以破蒙蔀如何。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纯粹至善。万理具焉。所谓性也。其感而发者情也。性无不善则从是性流出。宜无不善。此正先儒所谓浑沦说者。然则人之七情。浑沦说处。当以性发为言。而至若分开说处。不得不属之于气。试以退陶性情图考之。则中图是就理一边而言之。下图乃是兼理气而言之。中图之理一边。即下图所谓理乘之理也。来教所谓原于天命之性。而理乘之理。未尝有异于理发之理。诚的礭之论也。此退陶作图之义。愚之所谓中图拈出言之。下图分别言之。而其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来教以中图七情。谓之理发。下图七情。谓之气发。若尔则中图下图别为二情。而下图七情。全是气发。所谓理乘之理。将何处可寻乎。不但七情为然。中图之言性也。指其本然。下图之言性也。兼指其气质。亦将以本然气质。谓之各一其性者乎。来教以圣人七情之合于理者。谓之原于性命。奚独圣人有是哉。虽至
说及此。以取不韪之罪哉。但不能无疑于中者。玆敢不避僭猥而略言之。幸恕其狂妄而即赐批诲。以破蒙蔀如何。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纯粹至善。万理具焉。所谓性也。其感而发者情也。性无不善则从是性流出。宜无不善。此正先儒所谓浑沦说者。然则人之七情。浑沦说处。当以性发为言。而至若分开说处。不得不属之于气。试以退陶性情图考之。则中图是就理一边而言之。下图乃是兼理气而言之。中图之理一边。即下图所谓理乘之理也。来教所谓原于天命之性。而理乘之理。未尝有异于理发之理。诚的礭之论也。此退陶作图之义。愚之所谓中图拈出言之。下图分别言之。而其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来教以中图七情。谓之理发。下图七情。谓之气发。若尔则中图下图别为二情。而下图七情。全是气发。所谓理乘之理。将何处可寻乎。不但七情为然。中图之言性也。指其本然。下图之言性也。兼指其气质。亦将以本然气质。谓之各一其性者乎。来教以圣人七情之合于理者。谓之原于性命。奚独圣人有是哉。虽至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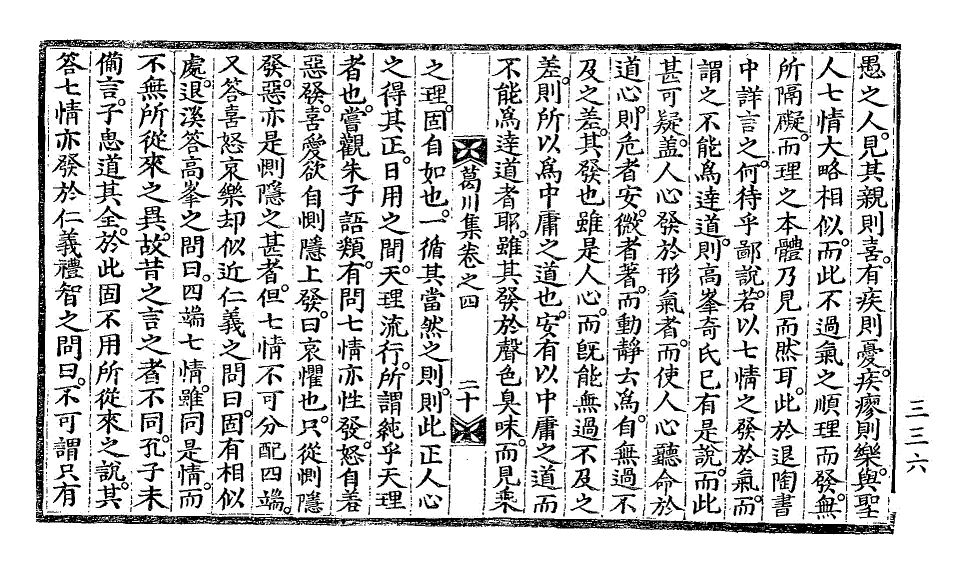 愚之人。见其亲则喜。有疾则忧。疾瘳则乐。与圣人七情大略相似。而此不过气之顺理而发。无所隔碍。而理之本体乃见而然耳。此于退陶书中详言之。何待乎鄙说。若以七情之发于气。而谓之不能为达道。则高峰奇氏已有是说。而此甚可疑。盖人心发于形气者。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其发也虽是人心。而既能无过不及之差。则所以为中庸之道也。安有以中庸之道而不能为达道者耶。虽其发于声色臭味。而见乘之理。固自如也。一循其当然之则。则此正人心之得其正。日用之间。天理流行。所谓纯乎天理者也。尝观朱子语类。有问七情亦性发。怒自羞恶发。喜爱欲自恻隐上发。曰哀惧也。只从恻隐发。恶亦是恻隐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又答喜怒哀乐却似近仁义之问曰。固有相似处。退溪答高峰之问曰。四端七情。虽同是情。而不无所从来之异。故昔之言之者不同。孔子未备言。子思道其全。于此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其答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问曰。不可谓只有
愚之人。见其亲则喜。有疾则忧。疾瘳则乐。与圣人七情大略相似。而此不过气之顺理而发。无所隔碍。而理之本体乃见而然耳。此于退陶书中详言之。何待乎鄙说。若以七情之发于气。而谓之不能为达道。则高峰奇氏已有是说。而此甚可疑。盖人心发于形气者。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其发也虽是人心。而既能无过不及之差。则所以为中庸之道也。安有以中庸之道而不能为达道者耶。虽其发于声色臭味。而见乘之理。固自如也。一循其当然之则。则此正人心之得其正。日用之间。天理流行。所谓纯乎天理者也。尝观朱子语类。有问七情亦性发。怒自羞恶发。喜爱欲自恻隐上发。曰哀惧也。只从恻隐发。恶亦是恻隐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又答喜怒哀乐却似近仁义之问曰。固有相似处。退溪答高峰之问曰。四端七情。虽同是情。而不无所从来之异。故昔之言之者不同。孔子未备言。子思道其全。于此固不用所从来之说。其答七情亦发于仁义礼智之问曰。不可谓只有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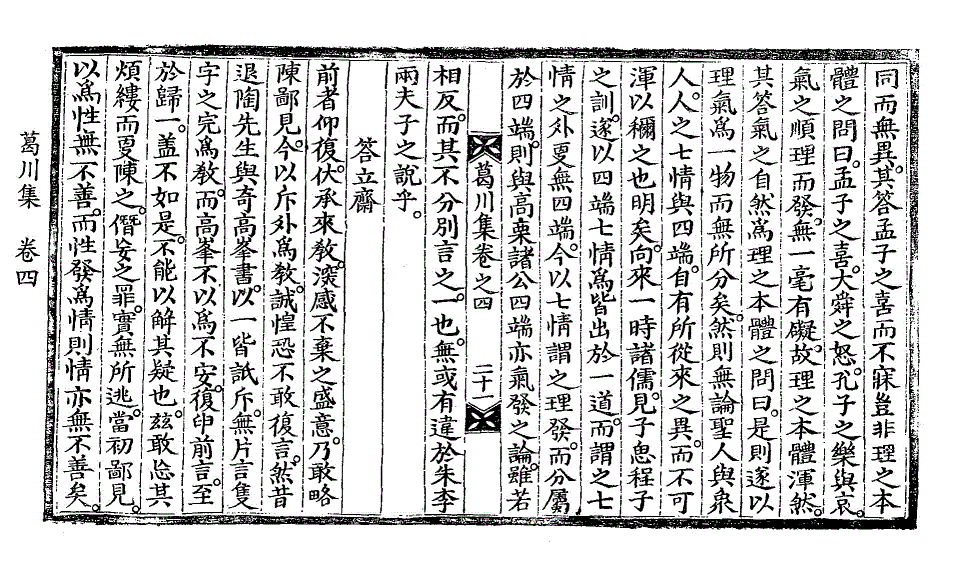 同而无异。其答孟子之喜而不寐岂非理之本体之问曰。孟子之喜。大舜之怒。孔子之乐与哀。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然。其答气之自然为理之本体之问曰。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分矣。然则无论圣人与众人。人之七情与四端。自有所从来之异。而不可浑以称之也明矣。向来一时诸儒。见子思程子之训。遂以四端七情为皆出于一道。而谓之七情之外更无四端。今以七情谓之理发。而分属于四端。则与高,栗诸公四端亦气发之论。虽若相反。而其不分别言之。一也。无或有违于朱李两夫子之说乎。
同而无异。其答孟子之喜而不寐岂非理之本体之问曰。孟子之喜。大舜之怒。孔子之乐与哀。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然。其答气之自然为理之本体之问曰。是则遂以理气为一物而无所分矣。然则无论圣人与众人。人之七情与四端。自有所从来之异。而不可浑以称之也明矣。向来一时诸儒。见子思程子之训。遂以四端七情为皆出于一道。而谓之七情之外更无四端。今以七情谓之理发。而分属于四端。则与高,栗诸公四端亦气发之论。虽若相反。而其不分别言之。一也。无或有违于朱李两夫子之说乎。答立斋
前者仰复。伏承来教。深感不弃之盛意。乃敢略陈鄙见。今以斥外为教。诚惶恐不敢复言。然昔退陶先生与奇高峰书。以一皆诋斥。无片言只字之完为教。而高峰不以为不安。复申前言。至于归一。盖不如是。不能以解其疑也。玆敢忘其烦缕而更陈之。僭妄之罪。实无所逃。当初鄙见。以为性无不善。而性发为情则情亦无不善矣。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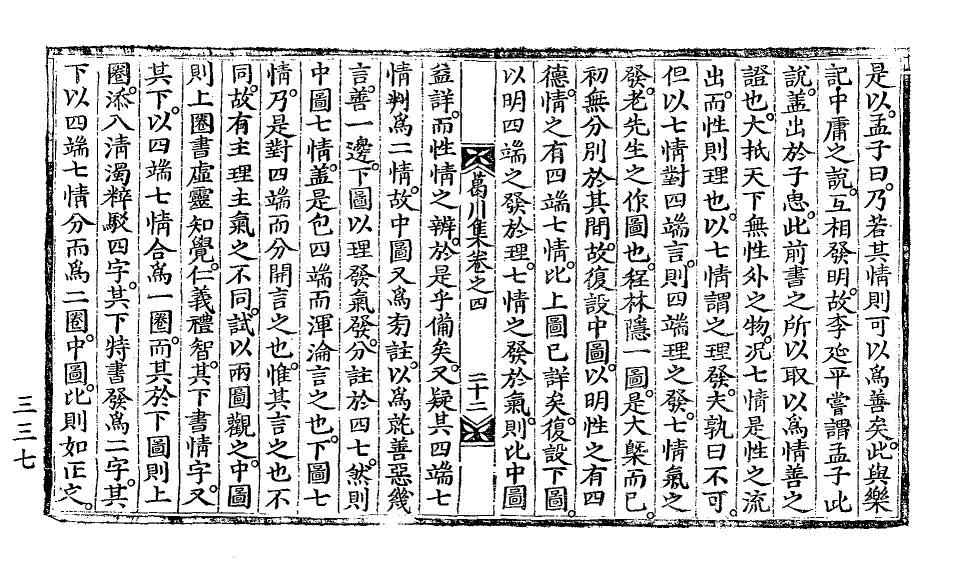 是以。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此与乐记,中庸之说。互相发明。故李延平尝谓孟子此说。盖出于子思。此前书之所以取以为情善之證也。大抵天下无性外之物。况七情是性之流出。而性则理也。以七情谓之理发。夫孰曰不可。但以七情对四端言。则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老先生之作图也。程林隐一图。是大槩而已。初无分别于其间。故复设中图。以明性之有四德。情之有四端七情。比上图已详矣。复设下图。以明四端之发于理。七情之发于气。则比中图益详。而性情之辨。于是乎备矣。又疑其四端七情判为二情。故中图又为旁注。以为就善恶几言。善一边。下图以理发气发。分注于四七。然则中图七情。盖是包四端而浑沦言之也。下图七情。乃是对四端而分开言之也。惟其言之也不同。故有主理主气之不同。试以两图观之。中图则上圈书虚灵知觉。仁义礼智。其下书情字。又其下。以四端七情合为一圈。而其于下图则上圈。添入清浊粹驳四字。其下特书发为二字。其下以四端七情分而为二圈。中图。比则如正文。
是以。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此与乐记,中庸之说。互相发明。故李延平尝谓孟子此说。盖出于子思。此前书之所以取以为情善之證也。大抵天下无性外之物。况七情是性之流出。而性则理也。以七情谓之理发。夫孰曰不可。但以七情对四端言。则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老先生之作图也。程林隐一图。是大槩而已。初无分别于其间。故复设中图。以明性之有四德。情之有四端七情。比上图已详矣。复设下图。以明四端之发于理。七情之发于气。则比中图益详。而性情之辨。于是乎备矣。又疑其四端七情判为二情。故中图又为旁注。以为就善恶几言。善一边。下图以理发气发。分注于四七。然则中图七情。盖是包四端而浑沦言之也。下图七情。乃是对四端而分开言之也。惟其言之也不同。故有主理主气之不同。试以两图观之。中图则上圈书虚灵知觉。仁义礼智。其下书情字。又其下。以四端七情合为一圈。而其于下图则上圈。添入清浊粹驳四字。其下特书发为二字。其下以四端七情分而为二圈。中图。比则如正文。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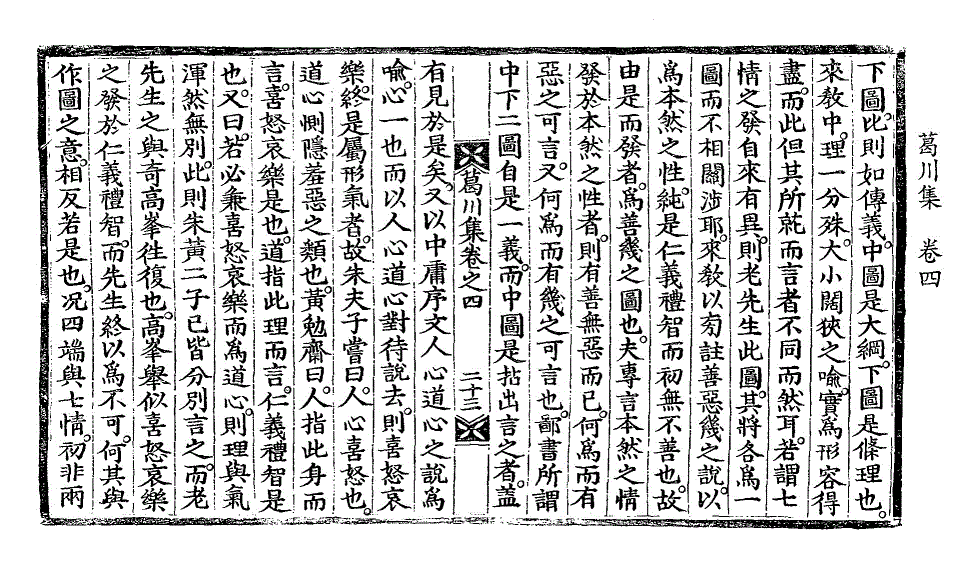 下图。比则如传义。中图是大纲。下图是条理也。来教中。理一分殊。大小阔狭之喻。实为形容得尽。而此但其所就而言者不同而然耳。若谓七情之发自来有异。则老先生此图。其将各为一图而不相关涉耶。来教以旁注善恶几之说。以为本然之性。纯是仁义礼智而初无不善也。故由是而发者。为善几之图也。夫专言本然之情发于本然之性者。则有善无恶而已。何为而有恶之可言。又何为而有几之可言也。鄙书所谓中下二图自是一义。而中图是拈出言之者。盖有见于是矣。又以中庸序文人心道心之说为喻。心一也而以人心道心对待说去。则喜怒哀乐。终是属形气者。故朱夫子尝曰。人心喜怒也。道心恻隐羞恶之类也。黄勉斋曰。人指此身而言。喜怒哀乐是也。道指此理而言。仁义礼智是也。又曰。若必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浑然无别。此则朱黄二子已皆分别言之。而老先生之与奇高峰往复也。高峰举似喜怒哀乐之发于仁义礼智。而先生终以为不可。何其与作图之意。相反若是也。况四端与七情。初非两
下图。比则如传义。中图是大纲。下图是条理也。来教中。理一分殊。大小阔狭之喻。实为形容得尽。而此但其所就而言者不同而然耳。若谓七情之发自来有异。则老先生此图。其将各为一图而不相关涉耶。来教以旁注善恶几之说。以为本然之性。纯是仁义礼智而初无不善也。故由是而发者。为善几之图也。夫专言本然之情发于本然之性者。则有善无恶而已。何为而有恶之可言。又何为而有几之可言也。鄙书所谓中下二图自是一义。而中图是拈出言之者。盖有见于是矣。又以中庸序文人心道心之说为喻。心一也而以人心道心对待说去。则喜怒哀乐。终是属形气者。故朱夫子尝曰。人心喜怒也。道心恻隐羞恶之类也。黄勉斋曰。人指此身而言。喜怒哀乐是也。道指此理而言。仁义礼智是也。又曰。若必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浑然无别。此则朱黄二子已皆分别言之。而老先生之与奇高峰往复也。高峰举似喜怒哀乐之发于仁义礼智。而先生终以为不可。何其与作图之意。相反若是也。况四端与七情。初非两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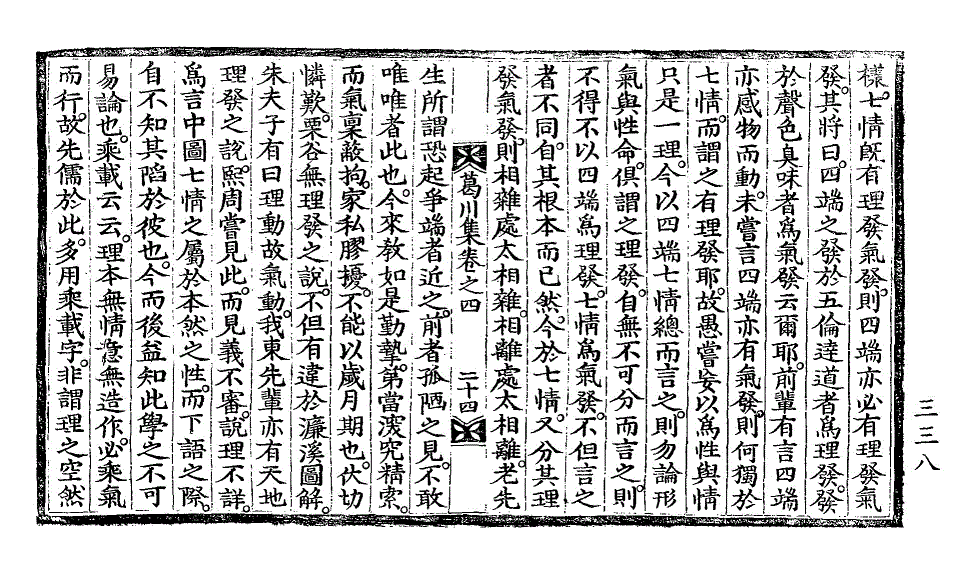 样。七情既有理发气发。则四端亦必有理发气发。其将曰。四端之发于五伦达道者为理发。发于声色臭味者为气发云尔耶。前辈有言四端亦感物而动。未尝言四端亦有气发。则何独于七情。而谓之有理发耶。故愚尝妄以为性与情只是一理。今以四端七情总而言之。则勿论形气与性命。俱谓之理发。自无不可分而言之。则不得不以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不但言之者不同。自其根本而已然。今于七情。又分其理发气发。则相杂处太相杂。相离处太相离。老先生所谓恐起争端者近之。前者孤陋之见。不敢唯唯者此也。今来教如是勤挚。第当深究精索。而气禀蔽拘。家私胶扰。不能以岁月期也。伏切怜叹。栗谷无理发之说。不但有违于濂溪图解。朱夫子有曰理动故气动。我东先辈亦有天地理发之说。熙周尝见此。而见义不审。说理不详。为言中图七情之属于本然之性。而下语之际。自不知其陷于彼也。今而后益知此学之不可易论也。乘载云云。理本无情意无造作。必乘气而行。故先儒于此。多用乘载字。非谓理之空然
样。七情既有理发气发。则四端亦必有理发气发。其将曰。四端之发于五伦达道者为理发。发于声色臭味者为气发云尔耶。前辈有言四端亦感物而动。未尝言四端亦有气发。则何独于七情。而谓之有理发耶。故愚尝妄以为性与情只是一理。今以四端七情总而言之。则勿论形气与性命。俱谓之理发。自无不可分而言之。则不得不以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不但言之者不同。自其根本而已然。今于七情。又分其理发气发。则相杂处太相杂。相离处太相离。老先生所谓恐起争端者近之。前者孤陋之见。不敢唯唯者此也。今来教如是勤挚。第当深究精索。而气禀蔽拘。家私胶扰。不能以岁月期也。伏切怜叹。栗谷无理发之说。不但有违于濂溪图解。朱夫子有曰理动故气动。我东先辈亦有天地理发之说。熙周尝见此。而见义不审。说理不详。为言中图七情之属于本然之性。而下语之际。自不知其陷于彼也。今而后益知此学之不可易论也。乘载云云。理本无情意无造作。必乘气而行。故先儒于此。多用乘载字。非谓理之空然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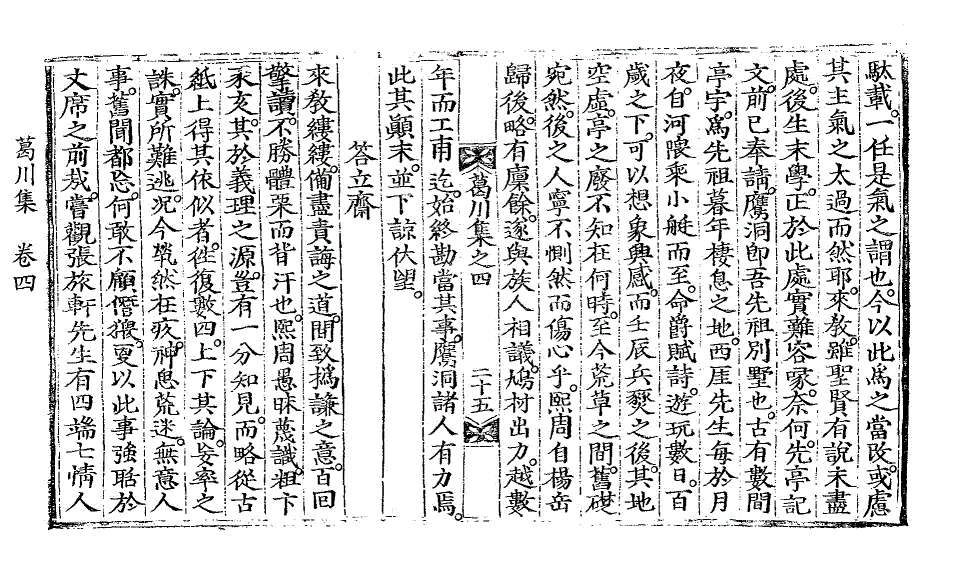 驮载。一任是气之谓也。今以此为之当改。或虑其主气之太过而然耶。来教。虽圣贤有说未尽处。后生末学。正于此处实难容喙。奈何。先亭记文。前已奉请。鹰洞即吾先祖别墅也。古有数间亭宇。为先祖暮年栖息之地。西厓先生每于月夜。自河隈乘小艇而至。命爵赋诗。游玩数日。百岁之下。可以想象兴感。而壬辰兵燹之后。其地空虚。亭之废不知在何时。至今荒草之间。旧础宛然。后之人宁不恻然而伤心乎。熙周自杨岳归后。略有廪馀。遂与族人相议。鸠材出力。越数年而工甫迄。始终勘当其事。鹰洞诸人有力焉。此其颠末。并下谅伏望。
驮载。一任是气之谓也。今以此为之当改。或虑其主气之太过而然耶。来教。虽圣贤有说未尽处。后生末学。正于此处实难容喙。奈何。先亭记文。前已奉请。鹰洞即吾先祖别墅也。古有数间亭宇。为先祖暮年栖息之地。西厓先生每于月夜。自河隈乘小艇而至。命爵赋诗。游玩数日。百岁之下。可以想象兴感。而壬辰兵燹之后。其地空虚。亭之废不知在何时。至今荒草之间。旧础宛然。后之人宁不恻然而伤心乎。熙周自杨岳归后。略有廪馀。遂与族人相议。鸠材出力。越数年而工甫迄。始终勘当其事。鹰洞诸人有力焉。此其颠末。并下谅伏望。答立斋
来教缕缕。备尽责诲之道。间致撝谦之意。百回擎读。不胜体栗而背汗也。熙周愚昧蔑识。粗卞豕亥。其于义理之源。岂有一分知见。而略从古纸上得其依似者。往复数四。上下其论。妄率之诛。实所难逃。况今煢然在疚。神思荒迷。无意人事。旧闻都忘。何敢不顾僭猥。更以此事强聒于丈席之前哉。尝观张旅轩先生有四端七情人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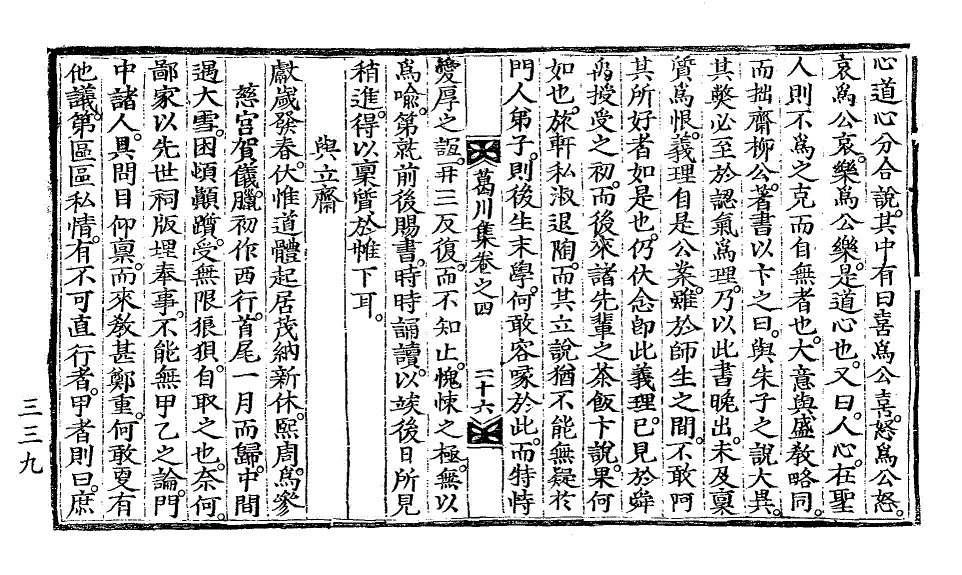 心道心分合说。其中有曰喜为公喜。怒为公怒。哀为公哀。乐为公乐。是道心也。又曰。人心。在圣人则不为之克而自无者也。大意与盛教略同。而拙斋柳公。著书以卞之曰。与朱子之说大异。其弊必至于认气为理。乃以此书晚出。未及禀质为恨。义理自是公案。虽于师生之间。不敢阿其所好者如是也。仍伏念即此义理。已见于舜禹授受之初。而后来诸先辈之茶饭卞说。果何如也。旅轩私淑退陶。而其立说犹不能无疑于门人弟子。则后生末学。何敢容喙于此。而特恃爱厚之谊。再三反复。而不知止。愧悚之极。无以为喻。第就前后赐书。时时诵读。以俟后日所见稍进。得以禀质于帷下耳。
心道心分合说。其中有曰喜为公喜。怒为公怒。哀为公哀。乐为公乐。是道心也。又曰。人心。在圣人则不为之克而自无者也。大意与盛教略同。而拙斋柳公。著书以卞之曰。与朱子之说大异。其弊必至于认气为理。乃以此书晚出。未及禀质为恨。义理自是公案。虽于师生之间。不敢阿其所好者如是也。仍伏念即此义理。已见于舜禹授受之初。而后来诸先辈之茶饭卞说。果何如也。旅轩私淑退陶。而其立说犹不能无疑于门人弟子。则后生末学。何敢容喙于此。而特恃爱厚之谊。再三反复。而不知止。愧悚之极。无以为喻。第就前后赐书。时时诵读。以俟后日所见稍进。得以禀质于帷下耳。与立斋
献岁发春。伏惟道体起居茂纳新休。熙周。为参 慈宫贺仪。腊初作西行。首尾一月而归。中间遇大雪。困顿颠踬。受无限狼狈。自取之也。奈何。鄙家以先世祠版埋奉事。不能无甲乙之论。门中诸人。具问目仰禀。而来教甚郑重。何敢更有他议。第区区私情。有不可直行者。甲者则曰。庶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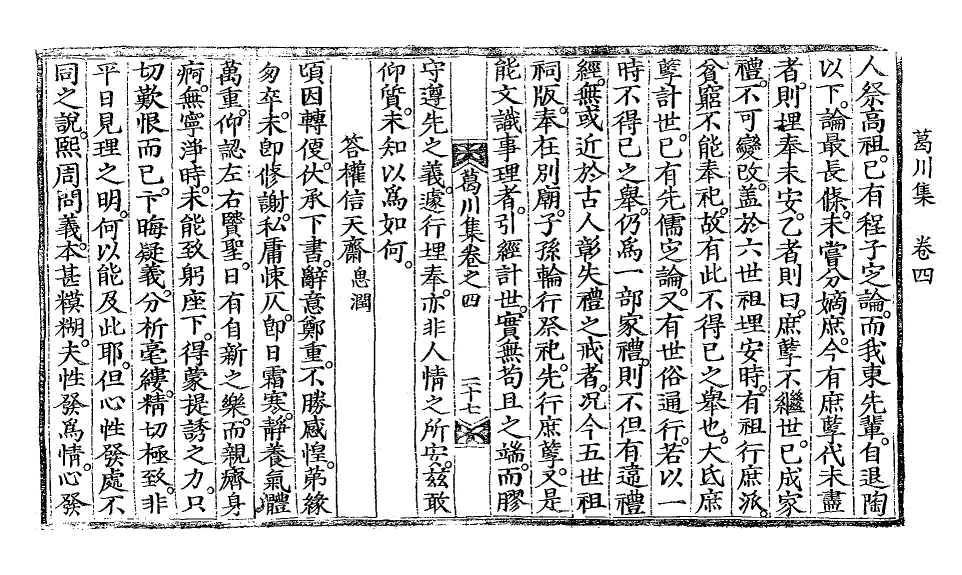 人祭高祖。已有程子定论。而我东先辈。自退陶以下。论最长条。未尝分嫡庶。今有庶孽代未尽者。则埋奉未安。乙者则曰。庶孽不继世。已成家礼。不可变改。盖于六世祖埋安时。有祖行庶派。贫穷不能奉祀。故有此不得已之举也。大氐庶孽计世。已有先儒定论。又有世俗通行。若以一时不得已之举。仍为一部家礼。则不但有违礼经。无或近于古人彰失礼之戒者。况今五世祖祠版。奉在别庙。子孙轮行祭祀。先行庶孽。又是能文识事理者。引经计世。实无苟且之端。而胶守遵先之义。遽行埋奉。亦非人情之所安。玆敢仰质。未知以为如何。
人祭高祖。已有程子定论。而我东先辈。自退陶以下。论最长条。未尝分嫡庶。今有庶孽代未尽者。则埋奉未安。乙者则曰。庶孽不继世。已成家礼。不可变改。盖于六世祖埋安时。有祖行庶派。贫穷不能奉祀。故有此不得已之举也。大氐庶孽计世。已有先儒定论。又有世俗通行。若以一时不得已之举。仍为一部家礼。则不但有违礼经。无或近于古人彰失礼之戒者。况今五世祖祠版。奉在别庙。子孙轮行祭祀。先行庶孽。又是能文识事理者。引经计世。实无苟且之端。而胶守遵先之义。遽行埋奉。亦非人情之所安。玆敢仰质。未知以为如何。答权信天斋(思润)
顷因转便。伏承下书。辞意郑重。不胜感惶。第缘匆卒。未即修谢。私庸悚仄。即日霜寒。静养气体万重。仰认左右贤圣。日有自新之乐。而亲癠身痾。无宁净时。未能致躬座下。得蒙提诱之力。只切叹恨而已。卞晦疑义。分析毫缕。精切极致。非平日见理之明。何以能及此耶。但心性发处不同之说。熙周问义。本甚模糊。夫性发为情。心发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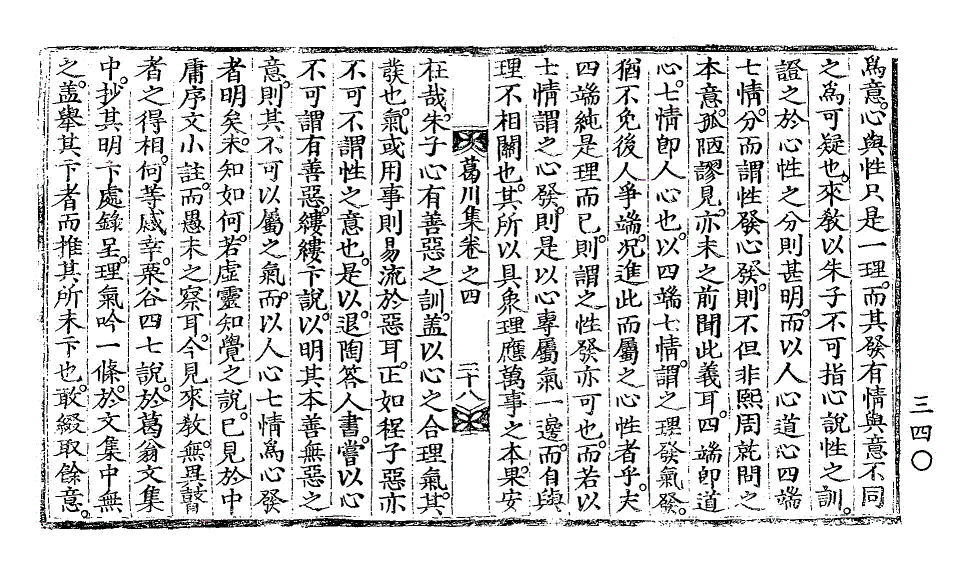 为意。心与性只是一理。而其发有情与意不同之为可疑也。来教以朱子不可指心说性之训。證之于心性之分则甚明。而以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分而谓性发心发。则不但非熙周就问之本意。孤陋谬见。亦未之前闻此义耳。四端即道心。七情即人心也。以四端七情。谓之理发气发。犹不免后人争端。况进此而属之心性者乎。夫四端纯是理而已。则谓之性发亦可也。而若以七情谓之心发。则是以心专属气一边。而自与理不相关也。其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之本。果安在哉。朱子心有善恶之训。盖以心之合理气。其发也。气或用事则易流于恶耳。正如程子恶亦不可不谓性之意也。是以。退陶答人书。尝以心不可谓有善恶。缕缕卞说。以明其本善无恶之意。则其不可以属之气。而以人心七情为心发者明矣。未知如何。若虚灵知觉之说。已见于中庸序文小注。而愚未之察耳。今见来教。无异瞽者之得相。何等感幸。栗谷四七说。于葛翁文集中。抄其明卞处录呈。理气吟一条。于文集中无之。盖举其卞者而推其所未卞也。敢缀取馀意。
为意。心与性只是一理。而其发有情与意不同之为可疑也。来教以朱子不可指心说性之训。證之于心性之分则甚明。而以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分而谓性发心发。则不但非熙周就问之本意。孤陋谬见。亦未之前闻此义耳。四端即道心。七情即人心也。以四端七情。谓之理发气发。犹不免后人争端。况进此而属之心性者乎。夫四端纯是理而已。则谓之性发亦可也。而若以七情谓之心发。则是以心专属气一边。而自与理不相关也。其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之本。果安在哉。朱子心有善恶之训。盖以心之合理气。其发也。气或用事则易流于恶耳。正如程子恶亦不可不谓性之意也。是以。退陶答人书。尝以心不可谓有善恶。缕缕卞说。以明其本善无恶之意。则其不可以属之气。而以人心七情为心发者明矣。未知如何。若虚灵知觉之说。已见于中庸序文小注。而愚未之察耳。今见来教。无异瞽者之得相。何等感幸。栗谷四七说。于葛翁文集中。抄其明卞处录呈。理气吟一条。于文集中无之。盖举其卞者而推其所未卞也。敢缀取馀意。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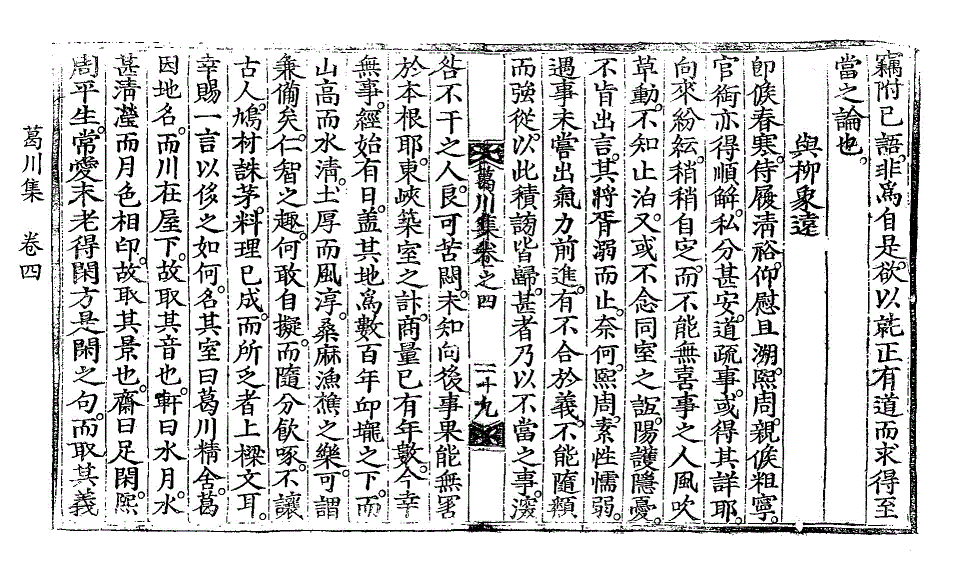 窃附己语。非为自是。欲以就正有道而求得至当之论也。
窃附己语。非为自是。欲以就正有道而求得至当之论也。与柳象远
即候春寒。侍履清裕。仰慰且溯。熙周。亲候粗宁。官衔亦得顺解。私分甚安。道疏事。或得其详耶。向来纷纭。稍稍自定。而不能无喜事之人风吹草动。不知止泊。又或不念同室之谊。阳护隐忧。不肯出言。其将胥溺而止。奈何。熙周。素性懦弱。遇事未尝出气力前进。有不合于义。不能随类而强从。以此积谤皆归。甚者乃以不当之事。深咎不干之人。良可苦闷。未知向后事果能无害于本根耶。东峡筑室之计。商量已有年数。今幸无事。经始有日。盖其地为数百年邱垄之下。而山高而水清。土厚而风淳。桑麻渔樵之乐。可谓兼备矣。仁智之趣。何敢自拟。而随分饮啄。不让古人。鸠材诛茅。料理已成。而所乏者上梁文耳。幸赐一言以侈之如何。名其室曰葛川精舍。葛因地名。而川在屋下。故取其音也。轩曰水月。水甚清滢而月色相印。故取其景也。斋曰足闲。熙周平生。常爱未老得闲方是闲之句。而取其义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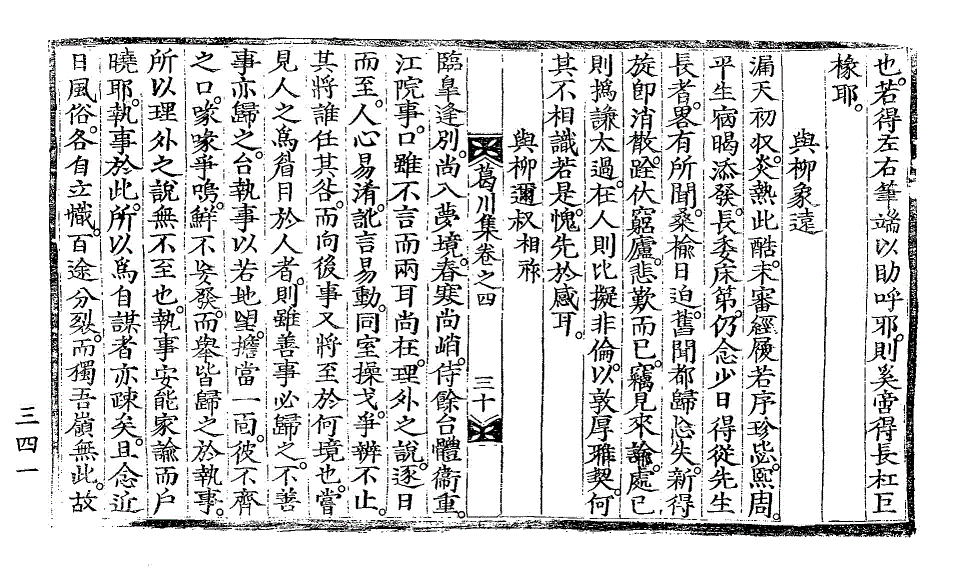 也。若得左右笔端以助呼邪。则奚啻得长杠巨椽耶。
也。若得左右笔端以助呼邪。则奚啻得长杠巨椽耶。与柳象远
漏天初收。炎热此酷。未审经履若序珍毖。熙周。平生宿暍添发。长委床笫。仍念少日得从先生长者。略有所闻。桑榆日迫。旧闻都归忘失。新得旋即消散。跧伏穷庐。悲叹而已。窃见来谕。处己则撝谦太过。在人则比拟非伦。以敦厚雅契。何其不相识若是。愧先于感耳。
与柳迩叔(저본의 원목차에는 '敬' 자로 되어 있다.相祚)
临皋逢别。尚入梦境。春寒尚峭。侍馀台体卫重。江院事。口虽不言而两耳尚在。理外之说。逐日而至。人心易淆。讹言易动。同室操戈。争辨不止。其将谁任其咎。而向后事又将至于何境也。尝见人之为眉目于人者。则虽善事必归之。不善事亦归之。台执事以若地望。担当一面。彼不齐之口。喙喙争鸣。鲜不妄发。而举皆归之于执事。所以理外之说无不至也。执事安能家谕而户晓耶。执事于此。所以为自谋者亦疏矣。且念近日风俗。各自立帜。百途分裂。而独吾岭无此。故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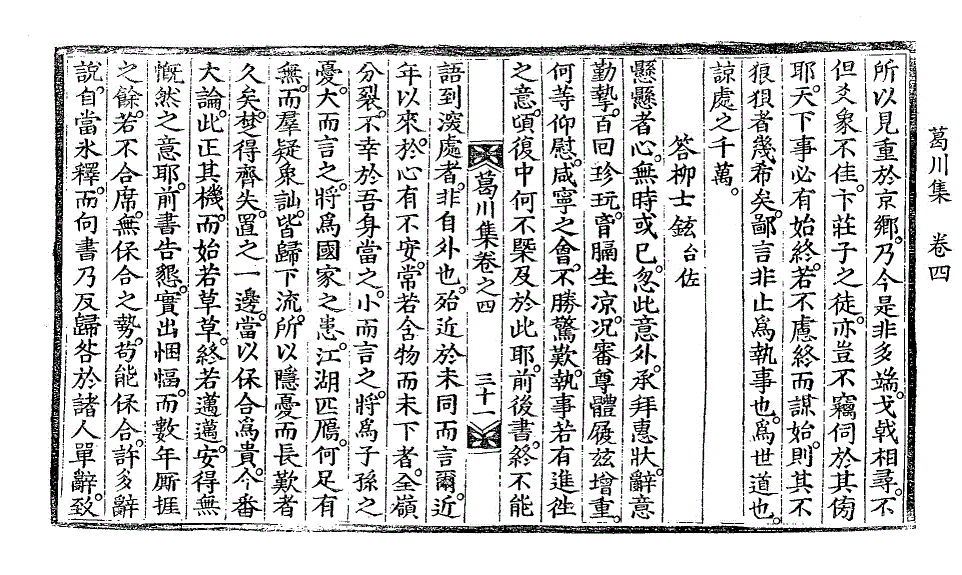 所以见重于京乡。乃今是非多端。戈戟相寻。不但爻象不佳。卞庄子之徒。亦岂不窃伺于其傍耶。天下事必有始终。若不虑终而谋始。则其不狼狈者几希矣。鄙言非止为执事也。为世道也。谅处之千万。
所以见重于京乡。乃今是非多端。戈戟相寻。不但爻象不佳。卞庄子之徒。亦岂不窃伺于其傍耶。天下事必有始终。若不虑终而谋始。则其不狼狈者几希矣。鄙言非止为执事也。为世道也。谅处之千万。答柳士铉(台佐)
悬悬者心。无时或已。忽此意外。承拜惠状。辞意勤挚。百回珍玩。胸膈生凉。况审尊体履玆增重。何等仰慰。咸宁之会。不胜惊叹。执事若有进往之意。顷复中何不槩及于此耶。前后书。终不能语到深处者。非自外也。殆近于未同而言尔。近年以来。于心有不安。常若含物而未下者。全岭分裂。不幸于吾身当之。小而言之。将为子孙之忧。大而言之。将为国家之患。江湖匹雁。何足有无。而群疑众讪。皆归下流。所以隐忧而长叹者久矣。楚得齐失。置之一边。当以保合为贵。今番大论。此正其机。而始若草草。终若迈迈。安得无慨然之意耶。前书告恳。实出悃愊。而数年厮挨之馀。若不合席。无保合之势。苟能保合。许多辞说。自当冰释。而向书乃反归咎于诸人单辞。致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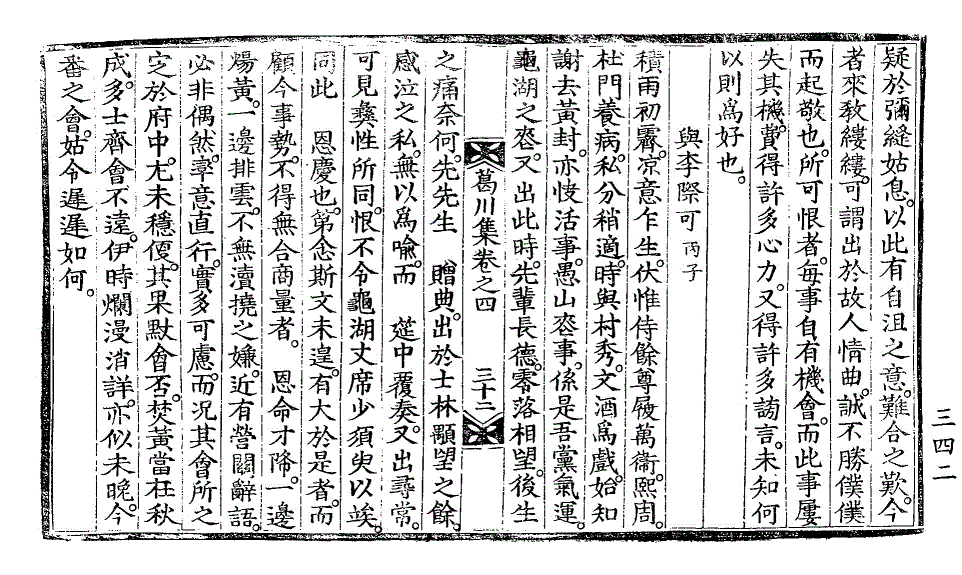 疑于弥缝姑息。以此有自沮之意。难合之叹。今者来教缕缕。可谓出于故人情曲。诚不胜仆仆而起敬也。所可恨者。每事自有机会。而此事屡失其机。费得许多心力。又得许多谤言。未知何以则为好也。
疑于弥缝姑息。以此有自沮之意。难合之叹。今者来教缕缕。可谓出于故人情曲。诚不胜仆仆而起敬也。所可恨者。每事自有机会。而此事屡失其机。费得许多心力。又得许多谤言。未知何以则为好也。与李际可(丙子)
积雨初霁。凉意乍生。伏惟侍馀尊履万卫。熙周。杜门养病。私分稍适。时与村秀。文酒为戏。始知谢去黄封。亦快活事。愚山丧事。系是吾党气运。龟湖之丧。又出此时。先辈长德。零落相望。后生之痛奈何。先先生 赠典。出于士林颙望之馀。感泣之私。无以为喻。而 筵中覆奏。又出寻常。可见彝性所同。恨不令龟湖丈席少须臾以俟。同此 恩庆也。第念斯文未遑。有大于是者。而顾今事势。不得无合商量者。 恩命才降。一边炀黄。一边排云。不无渎挠之嫌。近有营关辞语。必非偶然。率意直行。实多可虑。而况其会所之定于府中。尤未稳便。其果默会否。焚黄当在秋成。多士齐会不远。伊时烂漫消详。亦似未晚。今番之会。姑令迟迟如何。
答姜擎厦(橒○戊子)
岁暮穷巷。百感交中。此时清翰。不翅空谷跫音。仍审尊体起居每欠全安。为之虑仰。但静坐工夫。恰得朱晦翁盲废不早之意。然未发气象。乃是延平独得之见。才差失。不为吕氏之求中者几希。执事于此。无或易言耶。儿孙。常以襁褓儿视之。初不足与论名理。其茫昧固也。而来书褒奖太过。钳锤不足。是深介介耳。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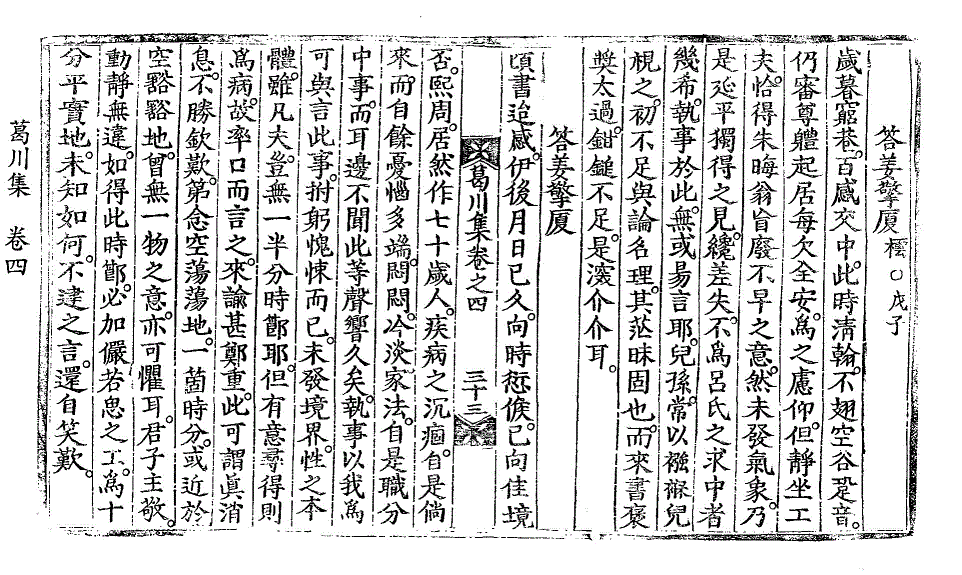 答姜擎厦
答姜擎厦顷书迨感。伊后月日已久。向时愆候。已向佳境否。熙周。居然作七十岁人。疾病之沉痼。自是倘来。而自馀忧恼多端。闷闷。冷淡。家法。自是职分中事。而耳边不闻此等声响久矣。执事以我为可与言此事。拊躬愧悚而已。未发境界。性之本体。虽凡夫。岂无一半分时节耶。但有意寻得则为病。故率口而言之。来谕甚郑重。此可谓真消息。不胜钦叹。第念空荡荡地。一个时分。或近于空豁豁地。曾无一物之意。亦可惧耳。君子主敬。动静无违。如得此时节。必加俨若思之工。为十分平实地。未知如何。不逮之言。还自笑叹。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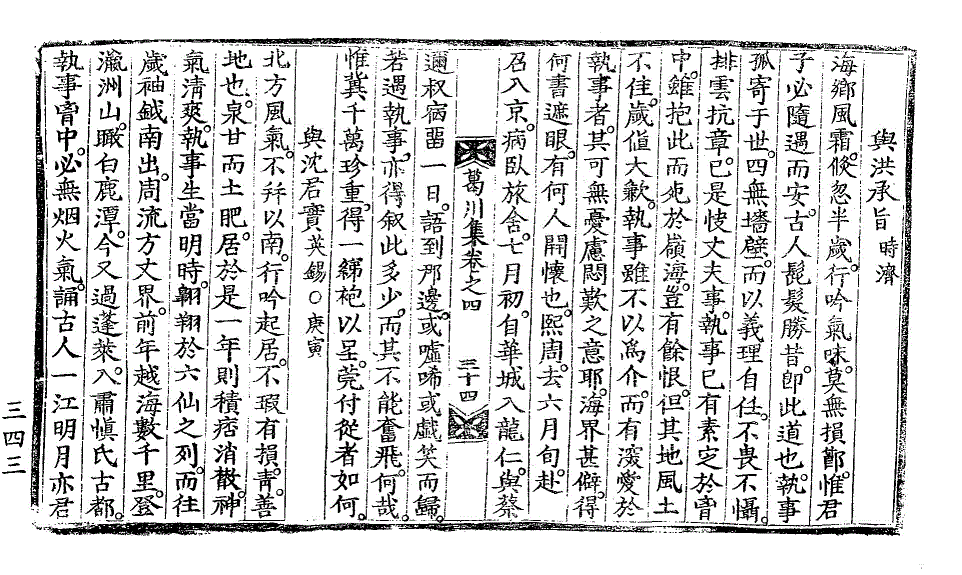 与洪承旨(时济)
与洪承旨(时济)海乡风霜。倏忽半岁。行吟气味。莫无损节。惟君子必随遇而安。古人髭发胜昔。即此道也。执事孤寄于世。四无墙壁。而以义理自任。不畏不慑。排云抗章。已是快丈夫事。执事已有素定于胸中。虽抱此而死于岭海。岂有馀恨。但其地风土不佳。岁值大歉。执事虽不以为介。而有深爱于执事者。其可无忧虑闷叹之意耶。海界甚僻。得何书遮眼。有何人开怀也。熙周。去六月旬。赴 召入京。病卧旅舍。七月初。自华城入龙仁。与蔡迩叔宿留一日。语到那边。或嘘唏或戏笑而归。若遇执事。亦得叙此多少。而其不能奋飞。何哉。惟冀千万珍重。得一绨袍以呈。莞付从者如何。
与沈君实(英锡○庚寅)
北方风气。不并以南。行吟起居。不瑕有损。青。善地也。泉甘而土肥。居于是一年则积痞消散。神气清爽。执事生当明时。翱翔于六仙之列。而往岁袖钺南出。周流方丈界。前年越海数千里。登瀛洲山。瞰白鹿潭。今又过蓬莱。入肃慎氏古都。执事胸中。必无烟火气。诵古人一江明月亦君
葛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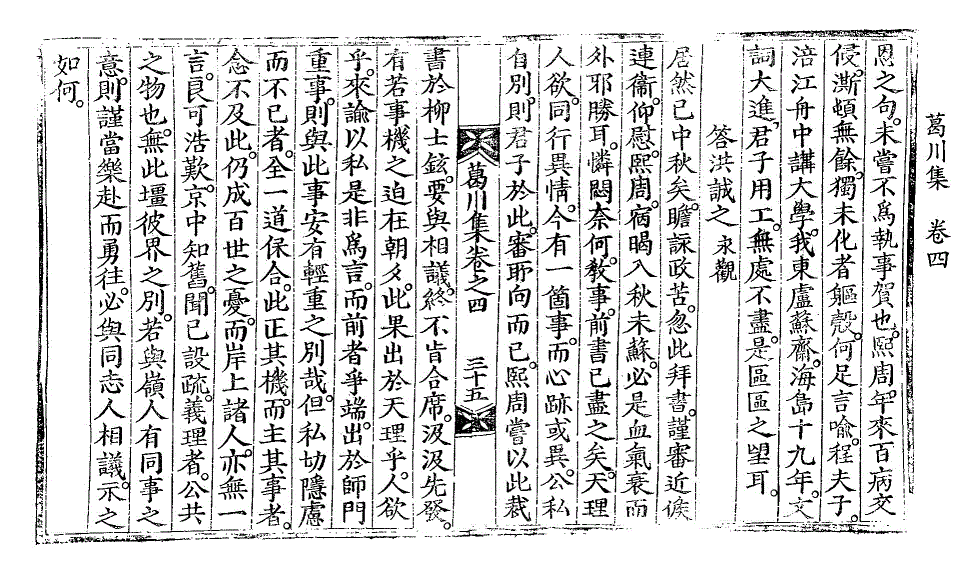 恩之句。未尝不为执事贺也。熙周。年来百病交侵。澌顿无馀。独未化者躯壳。何足言喻。程夫子。涪江舟中讲大学。我东卢苏斋。海岛十九年。文词大进。君子用工。无处不尽。是区区之望耳。
恩之句。未尝不为执事贺也。熙周。年来百病交侵。澌顿无馀。独未化者躯壳。何足言喻。程夫子。涪江舟中讲大学。我东卢苏斋。海岛十九年。文词大进。君子用工。无处不尽。是区区之望耳。答洪诚之(永观)
居然已中秋矣。瞻咏政苦。忽此拜书。谨审近候连卫。仰慰。熙周。宿暍入秋未苏。必是血气衰而外邪胜耳。怜闷奈何。教事。前书已尽之矣。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今有一个事。而心迹或异。公私自别。则君子于此。审所向而已。熙周尝以此裁书于柳士铉。要与相议。终不肯合席。汲汲先发。有若事机之迫在朝夕。此果出于天理乎。人欲乎。来谕以私是非为言。而前者争端。出于师门重事。则与此事安有轻重之别哉。但私切隐虑而不已者。全一道保合。此正其机。而主其事者。念不及此。仍成百世之忧。而岸上诸人。亦无一言。良可浩叹。京中知旧。闻已设疏。义理者。公共之物也。无此疆彼界之别。若与岭人有同事之意。则谨当乐赴而勇往。必与同志人相议。示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