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西斋集卷之五 第 x 页
西斋集卷之五
书
书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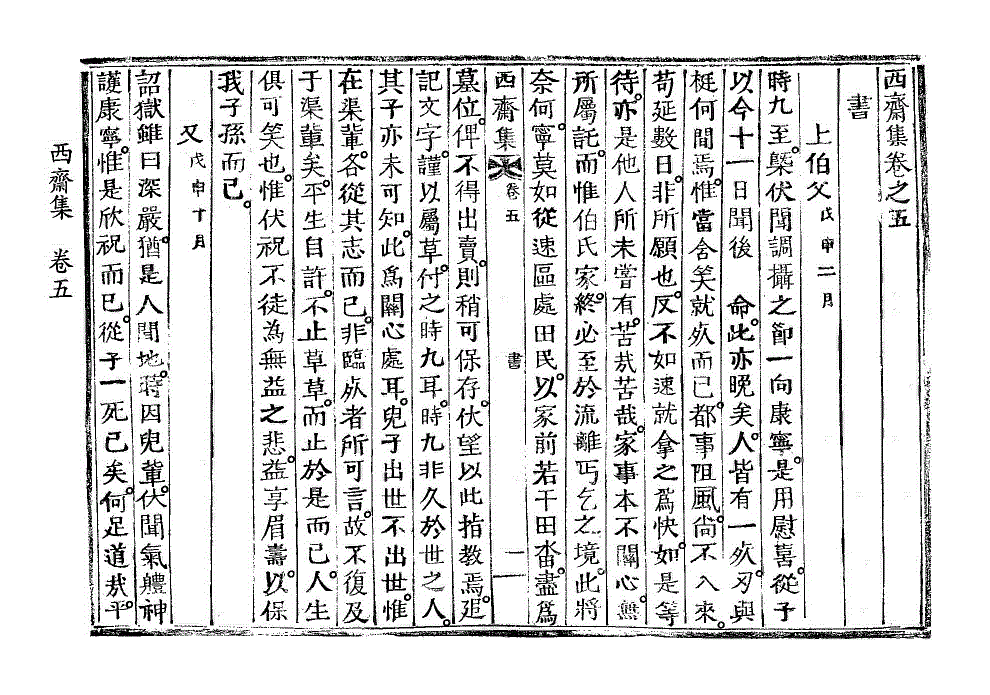 上伯父(戊申二月)
上伯父(戊申二月)时九至。槩伏闻调摄之节一向康宁。是用慰喜。从子以今十一日闻后 命。此亦晚矣。人皆有一死。刃与梃何间焉。惟当含笑就死而已。都事阻风。尚不入来。苟延数日。非所愿也。反不如速就拿之为快。如是等待。亦是他人所未尝有。苦哉苦哉。家事本不关心。无所属托。而惟伯氏家。终必至于流离丐乞之境。此将奈何。宁莫如从速区处田民。以家前若干田畓。尽为墓位。俾不得出卖。则稍可保存。伏望以此指教焉。追记文字。谨以属草。付之时九耳。时九非久于世之人。其子亦未可知。此为关心处耳。儿子出世不出世。惟在渠辈。各从其志而已。非临死者所可言。故不复及于渠辈矣。平生自许。不止草草。而止于是而已。人生俱可笑也。惟伏祝不徒为无益之悲。益享眉寿。以保我子孙而已。
上伯父(戊申十月)
诏狱虽曰深严。犹是人间地。时因儿辈。伏闻气体神护康宁。惟是欣祝而已。从子一死已矣。何足道哉。平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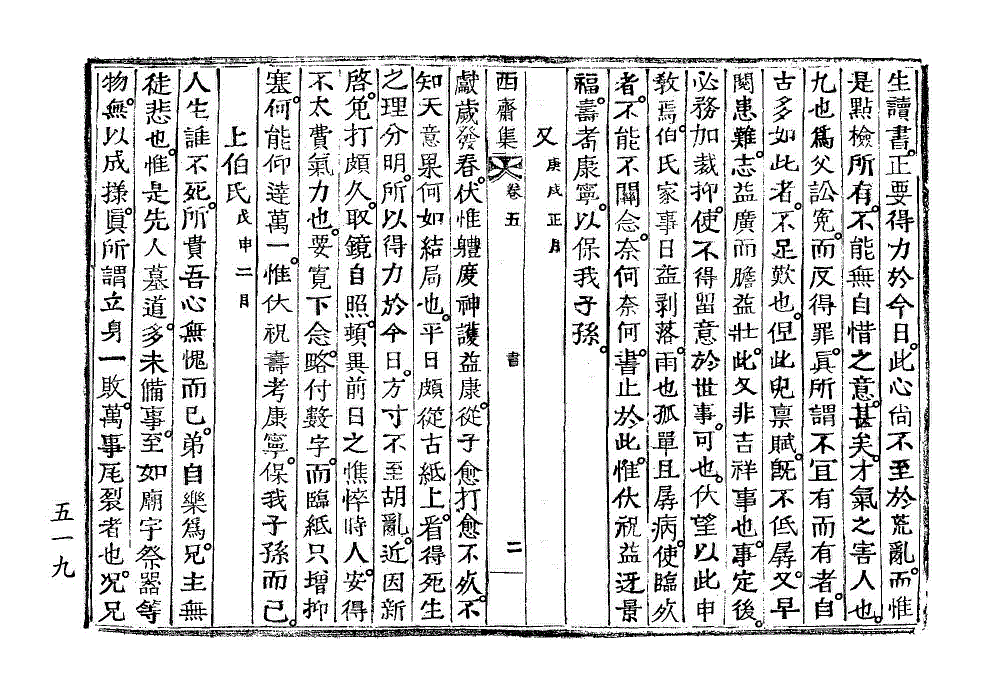 生读书。正要得力于今日。此心尚不至于荒乱。而惟是点检所有。不能无自惜之意。甚矣。才气之害人也。九也为父讼冤。而反得罪。真所谓不宜有而有者。自古多如此者。不足叹也。但此儿禀赋。既不低孱。又早阅患难。志益广而胆益壮。此又非吉祥事也。事定后。必务加裁抑。使不得留意于世事。可也。伏望以此申教焉。伯氏家事日益剥落。雨也孤单且孱病。使临死者。不能不关念。奈何奈何。书止于此。惟伏祝益迓景福。寿耇康宁。以保我子孙。
生读书。正要得力于今日。此心尚不至于荒乱。而惟是点检所有。不能无自惜之意。甚矣。才气之害人也。九也为父讼冤。而反得罪。真所谓不宜有而有者。自古多如此者。不足叹也。但此儿禀赋。既不低孱。又早阅患难。志益广而胆益壮。此又非吉祥事也。事定后。必务加裁抑。使不得留意于世事。可也。伏望以此申教焉。伯氏家事日益剥落。雨也孤单且孱病。使临死者。不能不关念。奈何奈何。书止于此。惟伏祝益迓景福。寿耇康宁。以保我子孙。上伯父(庚戌正月)
献岁发春。伏惟体度神护益康。从子愈打愈不死。不知天意果何如结局也。平日颇从古纸上。看得死生之理分明。所以得力于今日。方寸不至胡乱。近因新启。免打颇久。取镜自照。顿异前日之憔悴时人。安得不太费气力也。要宽下念。略付数字。而临纸只增抑塞。何能仰达万一。惟伏祝寿考康宁。保我子孙而已。
上伯氏(戊申二月)
人生谁不死。所贵吾心无愧而已。弟自乐为。兄主无徒悲也。惟是先人墓道。多未备事。至如庙宇祭器等物。无以成㨾。真所谓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者也。况兄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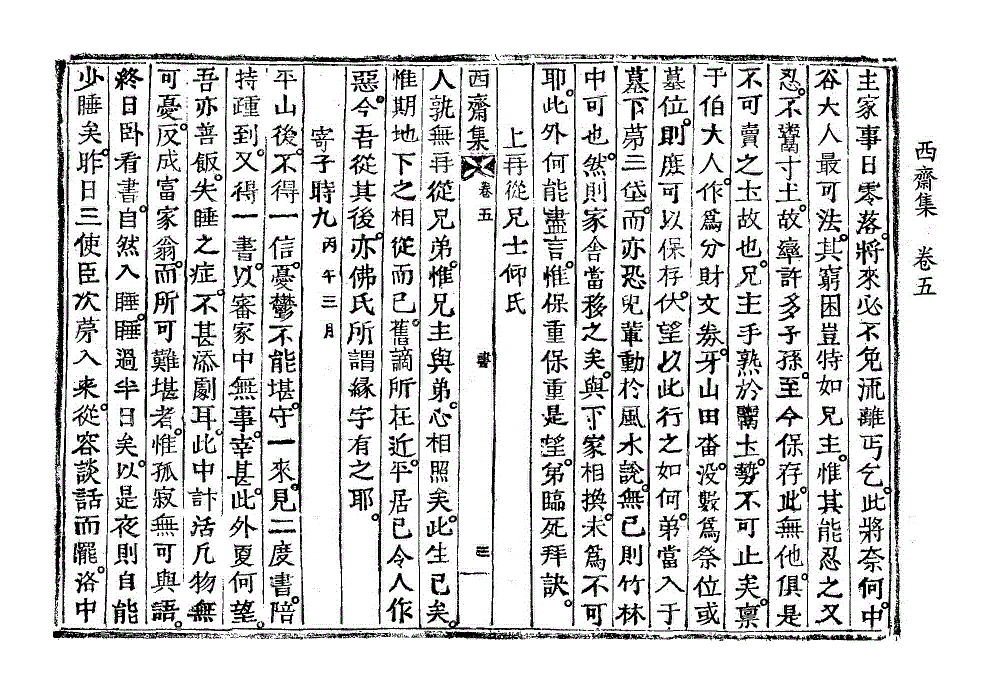 主家事日零落。将来必不免流离丐乞。此将奈何。中谷大人最可法。其穷困岂特如兄主。惟其能忍之又忍。不鬻寸土。故率许多子孙。至今保存。此无他。俱是不可卖之土故也。兄主手熟于鬻土。势不可止矣。禀于伯大人。作为分财文券。牙山田畓。没数为祭位或墓位。则庶可以保存。伏望以此行之如何。弟当入于墓下第三垈。而亦恐儿辈动于风水说。无已则竹林中可也。然则家舍当移之矣。与下家相换。未为不可耶。此外何能尽言。惟保重保重是望。弟临死拜诀。
主家事日零落。将来必不免流离丐乞。此将奈何。中谷大人最可法。其穷困岂特如兄主。惟其能忍之又忍。不鬻寸土。故率许多子孙。至今保存。此无他。俱是不可卖之土故也。兄主手熟于鬻土。势不可止矣。禀于伯大人。作为分财文券。牙山田畓。没数为祭位或墓位。则庶可以保存。伏望以此行之如何。弟当入于墓下第三垈。而亦恐儿辈动于风水说。无已则竹林中可也。然则家舍当移之矣。与下家相换。未为不可耶。此外何能尽言。惟保重保重是望。弟临死拜诀。上再从兄士仰氏
人孰无再从兄弟。惟兄主与弟。心相照矣。此生已矣。惟期地下之相从而已。旧谪所在近。平居已令人作恶。今吾从其后。亦佛氏所谓缘字有之耶。
寄子时九(丙午三月)
平山后。不得一信。忧郁不能堪。守一来。见二度书。陪持踵到。又得一书。以审家中无事。幸甚。此外更何望。吾亦善饭。失睡之症。不甚添剧耳。此中计活凡物无可忧。反成富家翁。而所可难堪者。惟孤寂无可与语。终日卧看书。自然入睡。睡过半日矣。以是夜则自能少睡矣。昨日三使臣次第入来。从容谈话而罢。洛中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0L 页
 何能多情。若是人情。真可笑也。 还收之启。不必久久相持。不如速停之为便。永甫不无意见矣。声甫疏。可谓明白痛快。实吾所欲言而不可得者。读之令人快阔。汝何看得不足耶。本事既尽卞破。吾则不期伸而自伸。何必救吾而后为得耶。立友又如汝言。甚乎。人之责人太重也。
何能多情。若是人情。真可笑也。 还收之启。不必久久相持。不如速停之为便。永甫不无意见矣。声甫疏。可谓明白痛快。实吾所欲言而不可得者。读之令人快阔。汝何看得不足耶。本事既尽卞破。吾则不期伸而自伸。何必救吾而后为得耶。立友又如汝言。甚乎。人之责人太重也。寄子时九(丙午十二月)
昨朝陪持来。见十六书。稍晚承奴至。见十日书。皆无事报也。可慰。而牙山患候。虽闻其向差。千里外忧虑。何可状言。汝则想已往觐矣。寒程驱驰。得无添病否。闻汝自遭今番事以后。浪费心虑。至欲忘寝。有时过饮。闻来不觉发笑也。今番事。岂其意外耶。况吾祸福。岂因此而有增减耶。世事每每如是泄泄。则吾虽十年二十年。不愿归矣。赖天之灵。 圣心一悟。而大臣有所变改时。则吾自南归矣。惟静而俟之而已。何足置诸胸里也。
寄子时九(丁未正月)
吾感气即解。而素有膈痰。故咳嗽有时发作。然本不足虑耳。向者 筵教。今始闻之。果是真的。则深紧益深。一倍惶懔。然万事在天。何用人力。击鼓甚无义意。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1H 页
 差待别有节拍。自有可为之时矣。大抵念疏后。一倍层加。念亦知此否。其疏洛中人多疑自吾出云。汝亦闻知否。安知此言不流入于 九重耶。起兄或入台地。则其意不欲随人浮沉。若有一别件事。上下必将为情外之疑矣。然岂有以是为虑乎。惟念门户单弱。不能自持。吾则已为世外人矣。万事都是此兄之责。而若又踵吾辙。则甚可惜也。须以勿学吾之意勉之也。如是而必欲为之。以前送二纸示之也。
差待别有节拍。自有可为之时矣。大抵念疏后。一倍层加。念亦知此否。其疏洛中人多疑自吾出云。汝亦闻知否。安知此言不流入于 九重耶。起兄或入台地。则其意不欲随人浮沉。若有一别件事。上下必将为情外之疑矣。然岂有以是为虑乎。惟念门户单弱。不能自持。吾则已为世外人矣。万事都是此兄之责。而若又踵吾辙。则甚可惜也。须以勿学吾之意勉之也。如是而必欲为之。以前送二纸示之也。寄诸子(丁未七月)
与汝等作别后。不过数里。此心已豁然无事。汝等虽不能如吾心之无事。亦不可径情自伤。以贻远去者之忧。须十分强定。母子相依为命可也。吾行今日始到林川。而气力日益健。怀抱亦自定。行役瘴海。俱不足为虑耳。重甫再昨到舒川。昨晓与其末弟还复出待于南塘。今早迎于林川北巷浦。与之同入榆村驿舍。叙话半饷。而婚事不可急急行礼。盖儿子道理。亦不可当此时入帐。其间亦有深长虑。不可预言故也。此后事。惟当一听其商量指挥。而无为催迫可也。擎病何如。此为不能忘之端耳。
寄诸子(丁未八月)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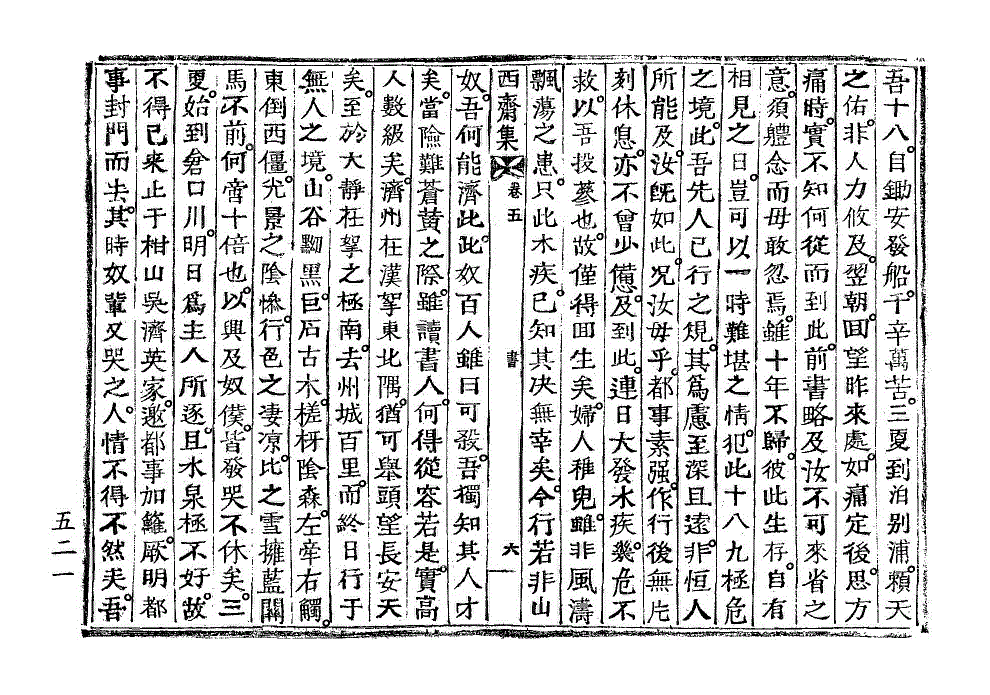 吾十八。自锄安发船。千辛万苦。三更到泊别浦。赖天之佑。非人力攸及。翌朝。回望昨来处。如痛定后。思方痛时。实不知何从而到此。前书略及汝不可来省之意。须体念而毋敢忽焉。虽十年不归。彼此生存。自有相见之日。岂可以一时难堪之情。犯此十八九极危之境。此吾先人已行之规。其为虑至深且远。非恒人所能及。汝既如此。况汝母乎。都事素强。作行后无片刻休息。亦不曾少惫。及到此。连日大发水疾。几危不救。以吾投蔘也。故仅得回生矣。妇人稚儿。虽非风涛飘荡之患。只此水疾。已知其决无幸矣。今行若非山奴。吾何能济此。此奴百人虽曰可杀。吾独知其人才矣。当险难苍黄之际。虽读书人。何得从容若是。实高人数级矣。济州在汉挐东北隅。犹可举头望长安天矣。至于大静在挐之极南。去州城百里。而终日行于无人之境。山谷黝黑。巨石古木。槎枒阴森。左牵右触。东倒西僵。光景之阴惨。行色之凄凉。比之雪拥蓝关马不前。何啻十倍也。以兴及奴仆。皆发哭不休矣。三更。始到仓口川。明日为主人所逐。且水泉极不好。故不得已来止于柑山吴济英家。邀都事加篱。厥明都事封门而去。其时奴辈又哭之。人情不得不然矣。吾
吾十八。自锄安发船。千辛万苦。三更到泊别浦。赖天之佑。非人力攸及。翌朝。回望昨来处。如痛定后。思方痛时。实不知何从而到此。前书略及汝不可来省之意。须体念而毋敢忽焉。虽十年不归。彼此生存。自有相见之日。岂可以一时难堪之情。犯此十八九极危之境。此吾先人已行之规。其为虑至深且远。非恒人所能及。汝既如此。况汝母乎。都事素强。作行后无片刻休息。亦不曾少惫。及到此。连日大发水疾。几危不救。以吾投蔘也。故仅得回生矣。妇人稚儿。虽非风涛飘荡之患。只此水疾。已知其决无幸矣。今行若非山奴。吾何能济此。此奴百人虽曰可杀。吾独知其人才矣。当险难苍黄之际。虽读书人。何得从容若是。实高人数级矣。济州在汉挐东北隅。犹可举头望长安天矣。至于大静在挐之极南。去州城百里。而终日行于无人之境。山谷黝黑。巨石古木。槎枒阴森。左牵右触。东倒西僵。光景之阴惨。行色之凄凉。比之雪拥蓝关马不前。何啻十倍也。以兴及奴仆。皆发哭不休矣。三更。始到仓口川。明日为主人所逐。且水泉极不好。故不得已来止于柑山吴济英家。邀都事加篱。厥明都事封门而去。其时奴辈又哭之。人情不得不然矣。吾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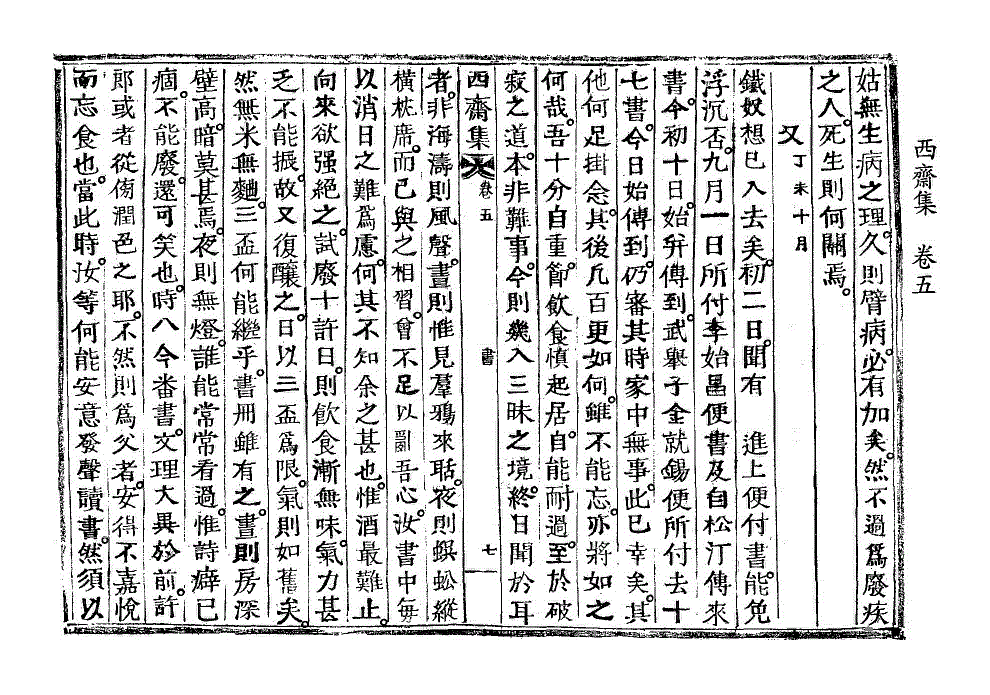 姑无生病之理。久则臂病。必有加矣。然不过为废疾之人。死生则何关焉。
姑无生病之理。久则臂病。必有加矣。然不过为废疾之人。死生则何关焉。寄诸子(丁未十月)
铁奴想已入去矣。初二日。闻有 进上便付书。能免浮沉否。九月一日所付李始昌便书及自松汀传来书。今初十日。始并传到。武举子金就锡便所付去十七书。今日始传到。仍审其时家中无事。此已幸矣。其他何足挂念。其后凡百更如何。虽不能忘。亦将如之何哉。吾十分自重。节饮食慎起居。自能耐过。至于破寂之道。本非难事。今则几入三昧之境。终日闻于耳者。非海涛则风声。昼则惟见群鸦来聒。夜则蜈蚣纵横枕席。而已与之相习。曾不足以乱吾心。汝书中每以消日之难为虑。何其不知余之甚也。惟酒最难止。向来欲强绝之。试废十许日。则饮食渐无味。气力甚乏不能振。故又复酿之。日以三杯为限。气则如旧矣。然无米无曲。三杯何能继乎。书册虽有之。昼则房深壁高。暗莫甚焉。夜则无灯。谁能常常看过。惟诗癖已痼。不能废。还可笑也。时八今番书。文理大异于前。许郎或者从傍润色之耶。不然则为父者。安得不嘉悦而忘食也。当此时。汝等何能安意发声读书。然须以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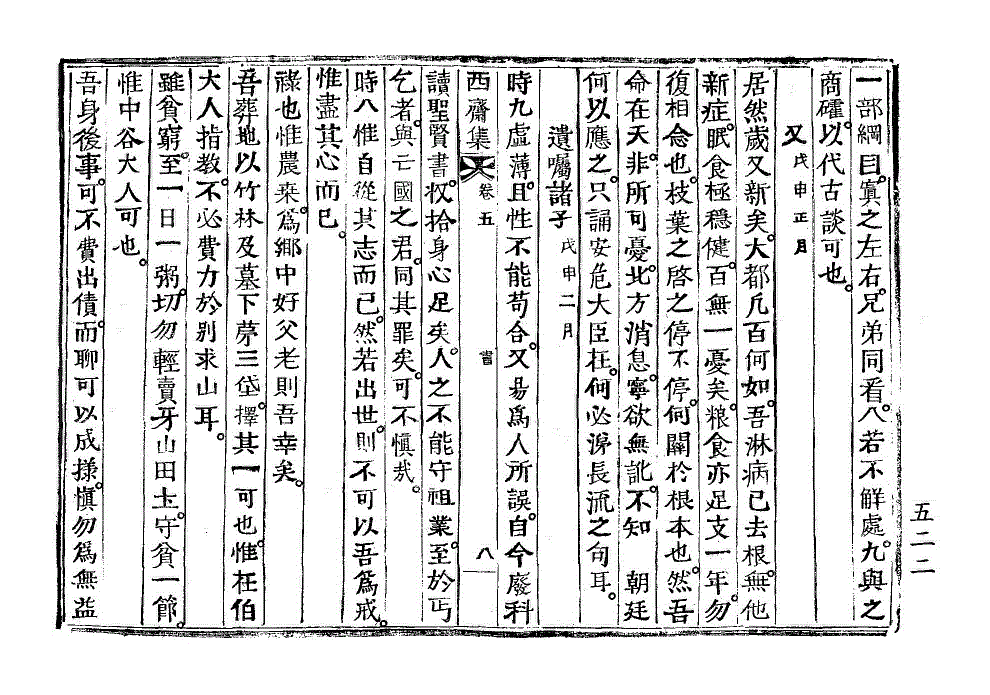 一部纲目。寘之左右。兄弟同看。八若不解处。九与之商礭。以代古谈可也。
一部纲目。寘之左右。兄弟同看。八若不解处。九与之商礭。以代古谈可也。寄诸子(戊申正月)
居然岁又新矣。大都凡百何如。吾淋病已去根。无他新症。眠食极稳健。百无一忧矣。粮食亦足支一年。勿复相念也。枝叶之启之停不停。何关于根本也。然吾命在天。非所可忧。北方消息。宁欲无讹。不知 朝廷何以应之。只诵安危大臣在。何必涕长流之句耳。
遗嘱诸子(戊申二月)
时九虚薄。且性不能苟合。又易为人所误。自今废科读圣贤书。收拾身心足矣。人之不能守祖业。至于丐乞者。与亡国之君。同其罪矣。可不慎哉。
时八惟自从其志而已。然若出世。则不可以吾为戒。惟尽其心而已。
禄也惟农桑。为乡中好父老则吾幸矣。
吾葬地以竹林及墓下第三垈。择其一可也。惟在伯大人指教。不必费力于别求山耳。
虽贫穷。至一日一粥。切勿轻卖牙山田土。守贫一节。惟中谷大人可也。
吾身后事。可不费出债。而聊可以成㨾。慎勿为无益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3H 页
 之事。勿费有限之财也。贫何足伤哉。但贫则不能不为分外之求。或至于多行不是事。取怨于乡邻。余为是惧。
之事。勿费有限之财也。贫何足伤哉。但贫则不能不为分外之求。或至于多行不是事。取怨于乡邻。余为是惧。吾自期甚不草草。而止于是。为 国之诚。不能效其万一。汝等其各尽心报 国。以继我志。
伯氏家必益穷。随事照管。无敢或忽。
外祖父母祠堂最为变礼难处矣。外孙奉祀。亦非礼。况外孙之子乎。况无称号者乎。须于三年后。与龙渊从叔相议变通。以为班袝之地可也。然吾先妣至意。吾未尝有一分奉行之道。此吾罪也。墓上无一片石。墓下无一寸土一指僮。此则为吾子之责也。然自存之不赡。何能及此。惟四人者轮回。数年一省。则可以答吾先妣之意也。
昔在庚子冬间。先君子复入台职。挺身担当。无所却顾。及论森事及 祭奠事。人莫不凛然危之。而先君子益思所以追报 肃考。誓一死于 国。不肖屡谏之不听。不肖计不知所出。时不肖新升六。始通台望。尝从容白曰。时人之待大人。亦薄矣。平时则惟恐枳塞之不力。及当此时。渠辈皆敛避。独使大人当之。不亦困乎。且大人老矣。讫可休矣。子虽不肖。亦已通籍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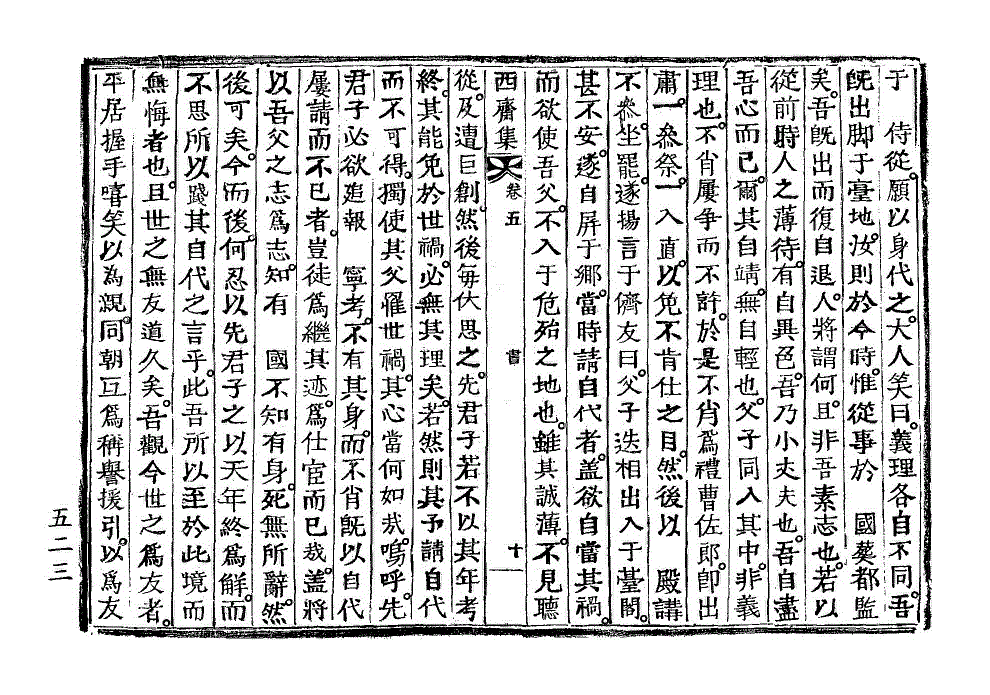 于 侍从。愿以身代之。大人笑曰。义理各自不同。吾既出脚于台地。汝则于今时。惟从事于 国葬都监矣。吾既出而复自退。人将谓何。且非吾素志也。若以从前时人之薄待。有自异色。吾乃小丈夫也。吾自尽吾心而已。尔其自靖。无自轻也。父子同入其中。非义理也。不肖屡争而不许。于是不肖为礼曹佐郎。即出肃。一参祭。一入直。以免不肯仕之目。然后以 殿讲不参。坐罢。遂扬言于侪友曰。父子迭相出入于台阁。甚不安。遂自屏于乡。当时请自代者。盖欲自当其祸。而欲使吾父。不入于危殆之地也。虽其诚薄。不见听从。及遭巨创。然后每伏思之。先君子若不以其年考终。其能免于世祸。必无其理矣。若然则其子请自代而不可得。独使其父罹世祸。其心当何如哉。呜呼。先君子必欲追报 宁考。不有其身。而不肖既以自代屡请而不已者。岂徒为继其迹。为仕宦而已哉。盖将以吾父之志为志。知有 国不知有身。死无所辞。然后可矣。今而后。何忍以先君子之以天年终为解。而不思所以践其自代之言乎。此吾所以至于此境而无悔者也。且世之无友道久矣。吾观今世之为友者。平居握手嘻笑以为亲。同朝互为称誉援引。以为友
于 侍从。愿以身代之。大人笑曰。义理各自不同。吾既出脚于台地。汝则于今时。惟从事于 国葬都监矣。吾既出而复自退。人将谓何。且非吾素志也。若以从前时人之薄待。有自异色。吾乃小丈夫也。吾自尽吾心而已。尔其自靖。无自轻也。父子同入其中。非义理也。不肖屡争而不许。于是不肖为礼曹佐郎。即出肃。一参祭。一入直。以免不肯仕之目。然后以 殿讲不参。坐罢。遂扬言于侪友曰。父子迭相出入于台阁。甚不安。遂自屏于乡。当时请自代者。盖欲自当其祸。而欲使吾父。不入于危殆之地也。虽其诚薄。不见听从。及遭巨创。然后每伏思之。先君子若不以其年考终。其能免于世祸。必无其理矣。若然则其子请自代而不可得。独使其父罹世祸。其心当何如哉。呜呼。先君子必欲追报 宁考。不有其身。而不肖既以自代屡请而不已者。岂徒为继其迹。为仕宦而已哉。盖将以吾父之志为志。知有 国不知有身。死无所辞。然后可矣。今而后。何忍以先君子之以天年终为解。而不思所以践其自代之言乎。此吾所以至于此境而无悔者也。且世之无友道久矣。吾观今世之为友者。平居握手嘻笑以为亲。同朝互为称誉援引。以为友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4H 页
 道。及有小利害。则鲜不为挤之。又下石之归矣。分谤犹未易得见。况分祸乎。吾王考与先君之于芝翁家。可谓无愧于死者矣。不肖每以此一节自勉。而恐无以充其操矣。当乙巳春间。余以丧人。为私家伸辨事入京。其时斯立首入台地。独当讨复事不少沮。而每就议于余。余虽丧人。乃其志则已誓于 国矣。何忍以丧人辞乎。遂为之相助。立亦非今世之人也。惟余言是听。其后闻之。一边人数吾侪中为罪者。惟以斯立首置杀秩。盖其势不得不然也。余思之。斯立果死于党人之手。是吾杀之也。吾虽无侠气。终不可死斯立而独生。余之所以极言他人之所不言者。盖欲突过斯立之上。以分斯立之祸也。果然时事变后。党人以余为第一。而立为第二矣。今则吾一人足以快党人心。斯立庶可免矣夫。于是乎吾无愧矣。无忝祖父矣。为吾子孙者。宜知此意也。
道。及有小利害。则鲜不为挤之。又下石之归矣。分谤犹未易得见。况分祸乎。吾王考与先君之于芝翁家。可谓无愧于死者矣。不肖每以此一节自勉。而恐无以充其操矣。当乙巳春间。余以丧人。为私家伸辨事入京。其时斯立首入台地。独当讨复事不少沮。而每就议于余。余虽丧人。乃其志则已誓于 国矣。何忍以丧人辞乎。遂为之相助。立亦非今世之人也。惟余言是听。其后闻之。一边人数吾侪中为罪者。惟以斯立首置杀秩。盖其势不得不然也。余思之。斯立果死于党人之手。是吾杀之也。吾虽无侠气。终不可死斯立而独生。余之所以极言他人之所不言者。盖欲突过斯立之上。以分斯立之祸也。果然时事变后。党人以余为第一。而立为第二矣。今则吾一人足以快党人心。斯立庶可免矣夫。于是乎吾无愧矣。无忝祖父矣。为吾子孙者。宜知此意也。寄子时九(以下在狱中书。戊申九月。)
固已虑矣。果然果然。然父子各以忠孝得罪。虽死何愧之有。吾决不以此为伤。须勿为虑。惟以自保千金。以持家门。为大义理可也。呜呼。上有宗祀。须汝承守。下有幼弟。须汝抚训。固不重欤。慎之慎之。汝禀赋实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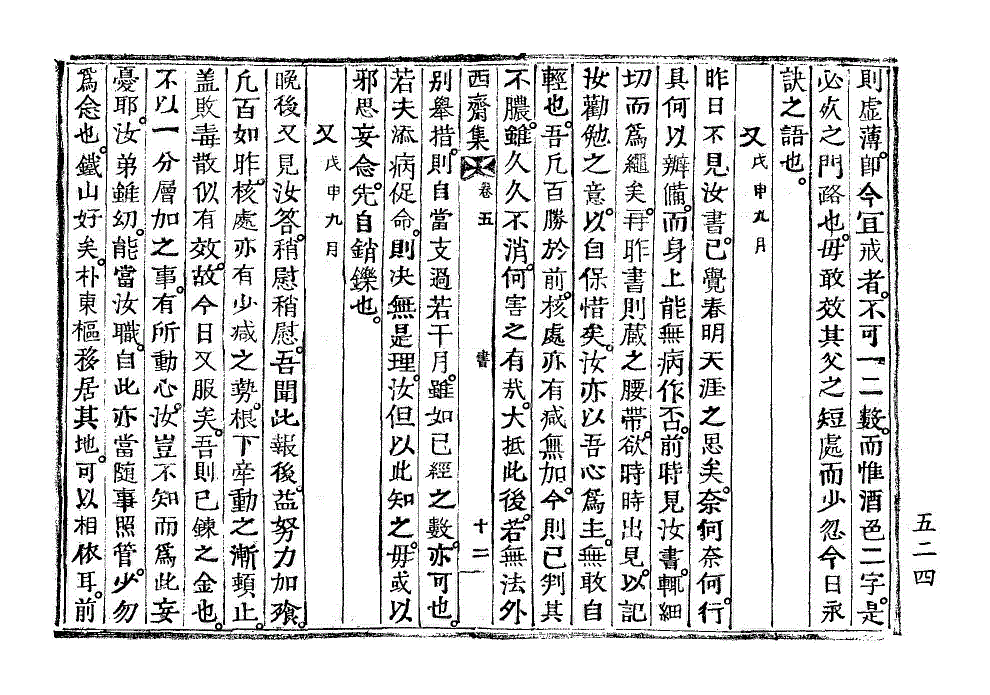 则虚薄。即今宜戒者。不可一二数。而惟酒色二字。是必死之门路也。毋敢效其父之短处而少忽今日永诀之语也。
则虚薄。即今宜戒者。不可一二数。而惟酒色二字。是必死之门路也。毋敢效其父之短处而少忽今日永诀之语也。寄子时九(戊申九月)
昨日不见汝书。已觉春明天涯之思矣。奈何奈何。行具何以办备。而身上能无病作否。前时见汝书。辄细切而为绳矣。再昨书则藏之腰带。欲时时出见。以记汝劝勉之意。以自保惜矣。汝亦以吾心为主。无敢自轻也。吾凡百胜于前。核处亦有减无加。今则已判其不脓。虽久久不消。何害之有哉。大抵此后。若无法外别举措。则自当支过若干月。虽如已经之数。亦可也。若夫添病促命。则决无是理。汝但以此知之。毋或以邪思妄念。先自销铄也。
寄子时九(戊申九月)
晚后又见汝答。稍慰稍慰。吾闻此报后。益努力加飧。凡百如昨。核处亦有少减之势。根下牵动之渐顿止。盖败毒散似有效。故今日又服矣。吾则已鍊之金也。不以一分层加之事。有所动心。汝岂不知而为此妄忧耶。汝弟虽幼。能当汝职。自此亦当随事照管。少勿为念也。铁山好矣。朴东枢移居其地。可以相依耳。前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5H 页
 日往来吾谪所者外。勿复接人可也。
日往来吾谪所者外。勿复接人可也。寄子时九(戊申九月)
汝行何其迟迟耶。虽留许多日。何益之有哉。不但其人之可畏。道理亦不当如是矣。须速前进也。汝念吾时。只自解曰。惟天在。彼辈于吾父何。只作如是念。则庶不至于丧心矣。至于消遣之道。当作何㨾。汝今日情地。不可如吾向日之迭荡。惟闭门看书可矣。而吾本无意劝汝等读书矣。然此则非所以为书也。只为消遣而已。须以一部史自随。熟看而略知古事可也。
寄子时九(戊申)
计已渡浿矣。吾则已忘之矣。何能使汝如吾之能忘之也。吾汝去后。再受杖。而此脚已成枯木顽石矣。不知痛苦。过后则神气辄胜于未过时。甚矣。其坚忍也。判付又例下而已。此后只当如过去事而已。汝亦但作如是观。勿生别念虑也。西塞风气甚烈。须避之如箭。日饮数三杯。而慎勿一时连举也。汝弟酬应凡百。能如成人。可喜可喜。
寄子时九(戊申十月)
铁亦是人间地。得见汝书。知汝得免颠仆道路。惟是幸也。此后事。只有苍苍在上。惟各尽自重之道。以待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5L 页
 彼定而已。何足伤心也。吾十一又经坐。而只是如前而已。近以堂上有故久免。而明间当又为坐云。数日前。以病重为手本。或得幸免耶。虽不免。不足惧矣。盖近间口味益胜。所食倍于平日。神气益爽然。若无别举措。则又将添一齿于此中矣。其间汝或蒙 恩先归。则何忧乎身后事也。核处无加无减。果是长寿之疾也。不必虑也。汝弟能当汝任。而但财力无出处。自汝去后。一府下人。其心皆变。理势当然。何足怪也。
彼定而已。何足伤心也。吾十一又经坐。而只是如前而已。近以堂上有故久免。而明间当又为坐云。数日前。以病重为手本。或得幸免耶。虽不免。不足惧矣。盖近间口味益胜。所食倍于平日。神气益爽然。若无别举措。则又将添一齿于此中矣。其间汝或蒙 恩先归。则何忧乎身后事也。核处无加无减。果是长寿之疾也。不必虑也。汝弟能当汝任。而但财力无出处。自汝去后。一府下人。其心皆变。理势当然。何足怪也。寄子时九(戊申十一月)
塞寒何能当。能自保如吾戒否。吾善饭稳眠。又久免。故凡百益胜。必能添一齿于此中矣。人谁不死。死而不死。古人所称。使汝能继吾志。养子孙以大吾门。则吾不死矣。勉之勉之。
寄子时九(戊申十一月)
昨得汝书。其末无月日。而臆料之。盖旬前出也。知汝能自保性命。惟此为幸。此外更何望。吾凡百。比汝去时大胜。此则久不坐之致也。抑天所以益困我也欤。东宫丧。罔极罔极。顾我亦旧时宫僚也。独不能服其服。只有吞声而哭而已。呜呼。生不如死矣。前已屡及矣。不复为勉戒之语。而观汝四祝诗。何其哀而至于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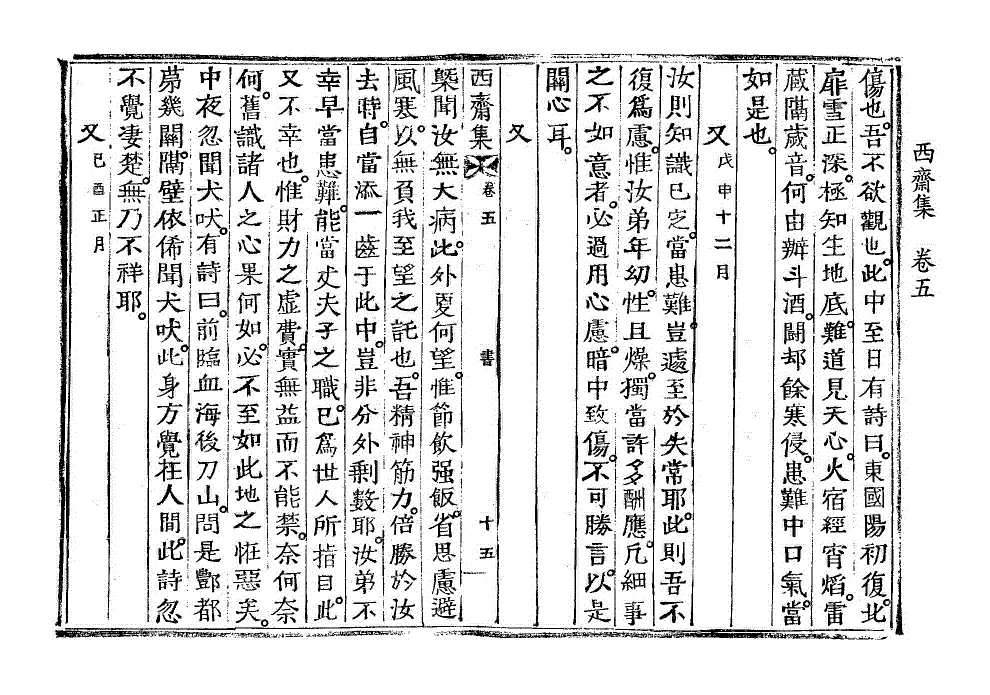 伤也。吾不欲观也。此中至日有诗曰。东国阳初复。北扉雪正深。极知生地底。难道见天心。火宿经宵焰。雷藏隔岁音。何由办斗酒。斗却馀寒侵。患难中口气。当如是也。
伤也。吾不欲观也。此中至日有诗曰。东国阳初复。北扉雪正深。极知生地底。难道见天心。火宿经宵焰。雷藏隔岁音。何由办斗酒。斗却馀寒侵。患难中口气。当如是也。寄子时九(戊申十二月)
汝则知识已定。当患难。岂遽至于失常耶。此则吾不复为虑。惟汝弟年幼。性且燥。独当许多酬应。凡细事之不如意者。必过用心虑。暗中致伤。不可胜言。以是关心耳。
寄子时九
槩闻汝无大病。此外更何望。惟节饮强饭。省思虑避风寒。以无负我至望之托也。吾精神筋力。倍胜于汝去时。自当添一齿于此中。岂非分外剩数耶。汝弟不幸早当患难。能当丈夫子之职。已为世人所指目。此又不幸也。惟财力之虚费。实无益而不能禁。奈何奈何。旧识诸人之心果何如。必不至如此地之怪恶矣。中夜忽闻犬吠。有诗曰。前临血海后刀山。问是酆都第几关。隔壁依俙闻犬吠。此身方觉在人间。此诗忽不觉凄楚。无乃不祥耶。
寄子时九(己酉正月)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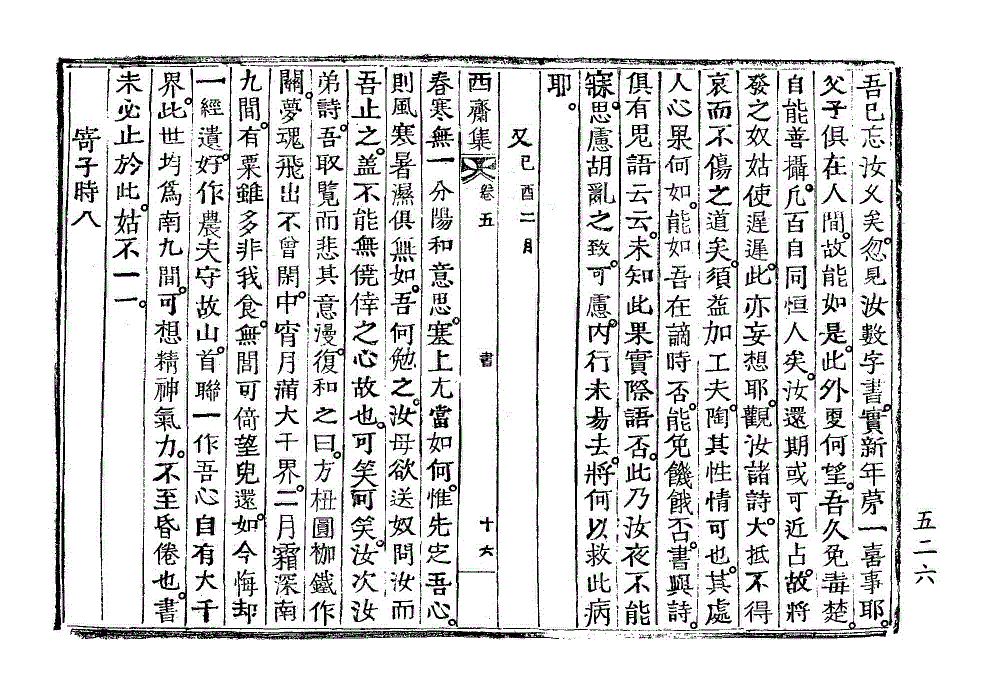 吾已忘汝久矣。忽见汝数字书。实新年第一喜事耶。父子俱在人间。故能如是。此外更何望。吾久免毒楚。自能善摄。凡百自同恒人矣。汝还期或可近占。故将发之奴姑使迟迟。此亦妄想耶。观汝诸诗。大抵不得哀而不伤之道矣。须益加工夫。陶其性情可也。其处人心果何如。能如吾在谪时否。能免饥饿否。书与诗。俱有鬼语云云。未知此果实际语否。此乃汝夜不能寐。思虑胡乱之致。可虑。内行未易去。将何以救此病耶。
吾已忘汝久矣。忽见汝数字书。实新年第一喜事耶。父子俱在人间。故能如是。此外更何望。吾久免毒楚。自能善摄。凡百自同恒人矣。汝还期或可近占。故将发之奴姑使迟迟。此亦妄想耶。观汝诸诗。大抵不得哀而不伤之道矣。须益加工夫。陶其性情可也。其处人心果何如。能如吾在谪时否。能免饥饿否。书与诗。俱有鬼语云云。未知此果实际语否。此乃汝夜不能寐。思虑胡乱之致。可虑。内行未易去。将何以救此病耶。寄子时九(己酉二月)
春寒无一分阳和意思。塞上尤当如何。惟先定吾心。则风寒暑湿俱无如。吾何勉之。汝母欲送奴问汝而吾止之。盖不能无侥倖之心故也。可笑可笑。汝次汝弟诗。吾取览而悲其意漫。复和之曰。方杻圆枷铁作关。梦魂飞出不曾闲。中宵月满大千界。二月霜深南九间。有粟虽多非我食。无闾可倚望儿还。如今悔却一经遗。好作农夫守故山。首联一作吾心自有大千界。此世均为南九间。可想精神气力。不至昏倦也。书未必止于此。姑不一一。
寄子时八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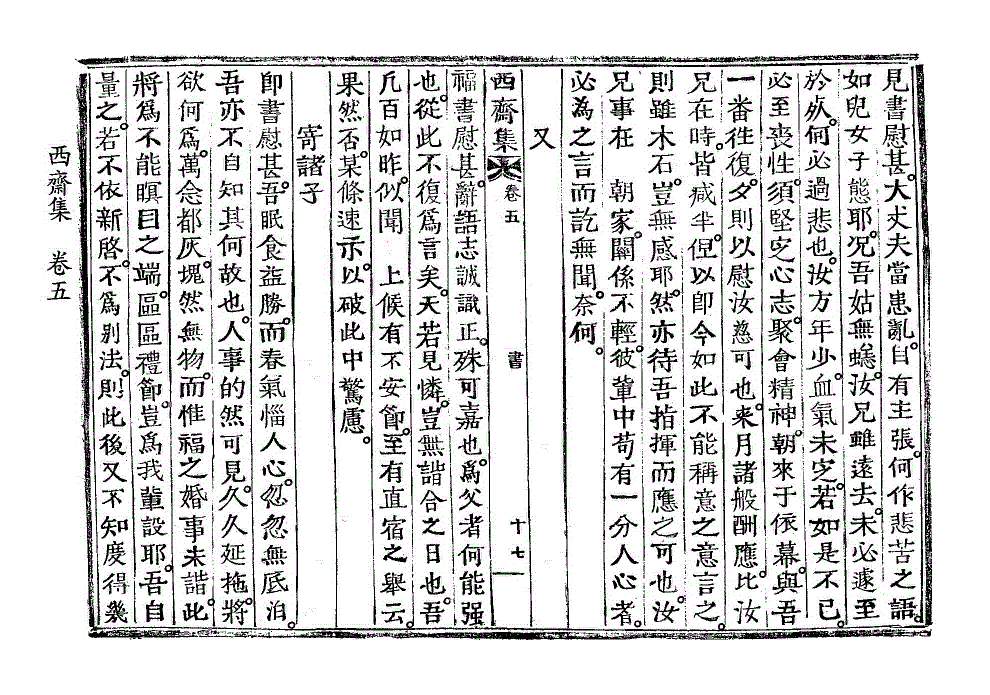 见书慰甚。大丈夫当患乱。自有主张。何作悲苦之语。如儿女子态耶。况吾姑无𧏮。汝兄虽远去。未必遽至于死。何必过悲也。汝方年少。血气未定。若如是不已。必至丧性。须坚定心志。聚会精神。朝来于依幕。与吾一番往复。夕则以慰汝慈可也。来月诸般酬应。比汝兄在时。皆减半。但以即今如此不能称意之意言之。则虽木石。岂无感耶。然亦待吾指挥而应之可也。汝兄事在 朝家。关系不轻。彼辈中苟有一分人心者。必为之言而讫无闻。奈何。
见书慰甚。大丈夫当患乱。自有主张。何作悲苦之语。如儿女子态耶。况吾姑无𧏮。汝兄虽远去。未必遽至于死。何必过悲也。汝方年少。血气未定。若如是不已。必至丧性。须坚定心志。聚会精神。朝来于依幕。与吾一番往复。夕则以慰汝慈可也。来月诸般酬应。比汝兄在时。皆减半。但以即今如此不能称意之意言之。则虽木石。岂无感耶。然亦待吾指挥而应之可也。汝兄事在 朝家。关系不轻。彼辈中苟有一分人心者。必为之言而讫无闻。奈何。寄子时八
福书慰甚。辞语志诚识正。殊可嘉也。为父者何能强也。从此不复为言矣。天若见怜。岂无谐合之日也。吾凡百如昨。似闻 上候有不安节。至有直宿之举云。果然否。某条速示。以破此中惊虑。
寄诸子
即书慰甚。吾眠食益胜。而春气恼人心。忽忽无厎泊。吾亦不自知其何故也。人事的然可见。久久延拖。将欲何为。万念都灰。块然无物。而惟福之婚事未谐。此将为不能瞑目之端。区区礼节。岂为我辈设耶。吾自量之。若不依新启。不为别法。则此后又不知度得几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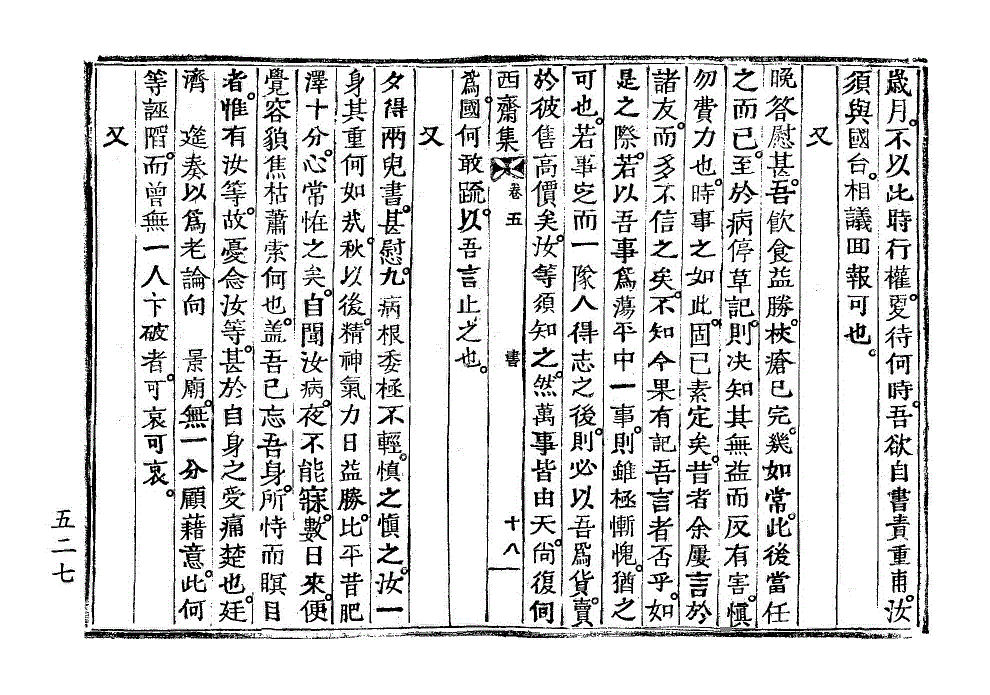 岁月。不以此时行权。更待何时。吾欲自书责重甫。汝须与国台。相议回报可也。
岁月。不以此时行权。更待何时。吾欲自书责重甫。汝须与国台。相议回报可也。寄诸子
晚答慰甚。吾饮食益胜。杖疮已完。几如常。此后当任之而已。至于病停草记。则决知其无益而反有害。慎勿费力也。时事之如此。固已素定矣。昔者余屡言于诸友。而多不信之矣。不知今果有记吾言者否乎。如是之际。若以吾事为荡平中一事。则虽极惭愧。犹之可也。若事定而一队人得志之后。则必以吾为货。卖于彼售高价矣。汝等须知之。然万事皆由天。尚复何为。国何敢疏。以吾言止之也。
寄诸子
夕得两儿书。甚慰。九病根委极不轻。慎之慎之。汝一身其重何如哉。秋以后。精神气力日益胜。比平昔肥泽十分。心常怪之矣。自闻汝病。夜不能寐。数日来。便觉容貌焦枯萧索何也。盖吾已忘吾身。所恃而瞑目者。惟有汝等。故忧念汝等。甚于自身之受痛楚也。廷济 筵奏以为老论向 景庙。无一分顾藉意。此何等诬陷。而曾无一人卞破者。可哀可哀。
寄诸子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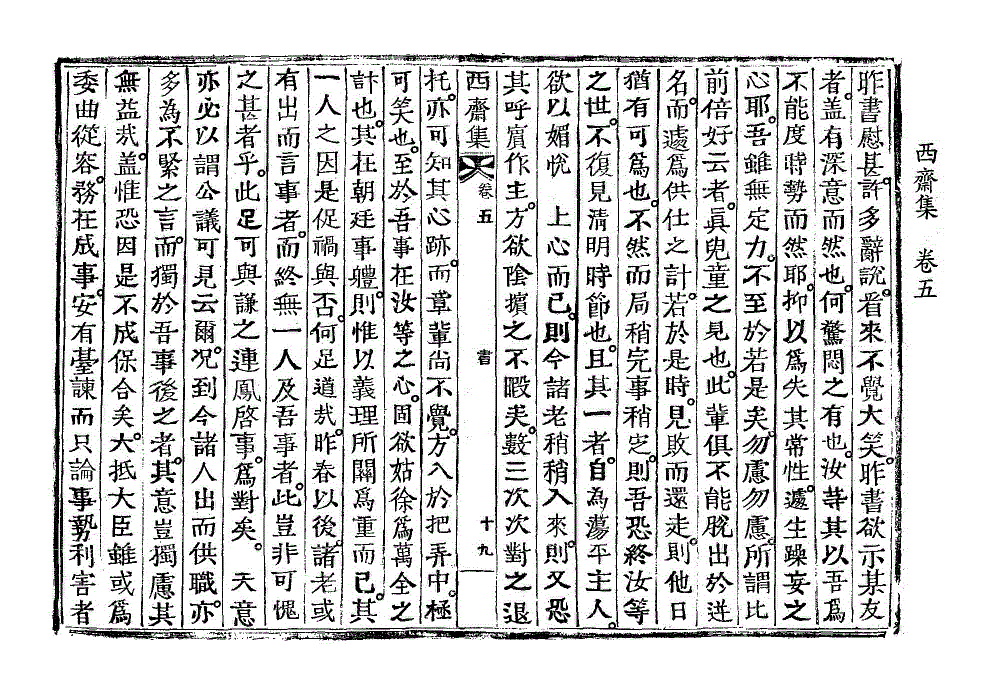 昨书慰甚。许多辞说。看来不觉大笑。昨书欲示某友者。盖有深意而然也。何惊闷之有也。汝等其以吾为不能度时势而然耶。抑以为失其常性。遽生躁妄之心耶。吾虽无定力。不至于若是矣。勿虑勿虑。所谓比前倍好云者。真儿童之见也。此辈俱不能脱出于逆名。而遽为供仕之计。若于是时。见败而还走。则他日犹有可为也。不然而局稍完事稍定。则吾恐终汝等之世。不复见清明时节也。且其一者。自为荡平主人。欲以媚悦 上心而已。则今诸老稍稍入来。则又恐其呼宾作主。方欲阴摈之不暇矣。数三次次对之退托。亦可知其心迹。而章辈尚不觉。方入于把弄中。极可笑也。至于吾事在汝等之心。固欲姑徐为万全之计也。其在朝廷事体。则惟以义理所关为重而已。其一人之因是促祸与否。何足道哉。昨春以后。诸老或有出而言事者。而终无一人及吾事者。此岂非可愧之甚者乎。此足可与谦之连凤启事。为对矣。 天意亦必以谓公议可见云尔。况到今诸人出而供职。亦多为不紧之言。而独于吾事后之者。其意岂独虑其无益哉。盖惟恐因是不成保合矣。大抵大臣虽或为委曲从容。务在成事。安有台谏而只论事势利害者
昨书慰甚。许多辞说。看来不觉大笑。昨书欲示某友者。盖有深意而然也。何惊闷之有也。汝等其以吾为不能度时势而然耶。抑以为失其常性。遽生躁妄之心耶。吾虽无定力。不至于若是矣。勿虑勿虑。所谓比前倍好云者。真儿童之见也。此辈俱不能脱出于逆名。而遽为供仕之计。若于是时。见败而还走。则他日犹有可为也。不然而局稍完事稍定。则吾恐终汝等之世。不复见清明时节也。且其一者。自为荡平主人。欲以媚悦 上心而已。则今诸老稍稍入来。则又恐其呼宾作主。方欲阴摈之不暇矣。数三次次对之退托。亦可知其心迹。而章辈尚不觉。方入于把弄中。极可笑也。至于吾事在汝等之心。固欲姑徐为万全之计也。其在朝廷事体。则惟以义理所关为重而已。其一人之因是促祸与否。何足道哉。昨春以后。诸老或有出而言事者。而终无一人及吾事者。此岂非可愧之甚者乎。此足可与谦之连凤启事。为对矣。 天意亦必以谓公议可见云尔。况到今诸人出而供职。亦多为不紧之言。而独于吾事后之者。其意岂独虑其无益哉。盖惟恐因是不成保合矣。大抵大臣虽或为委曲从容。务在成事。安有台谏而只论事势利害者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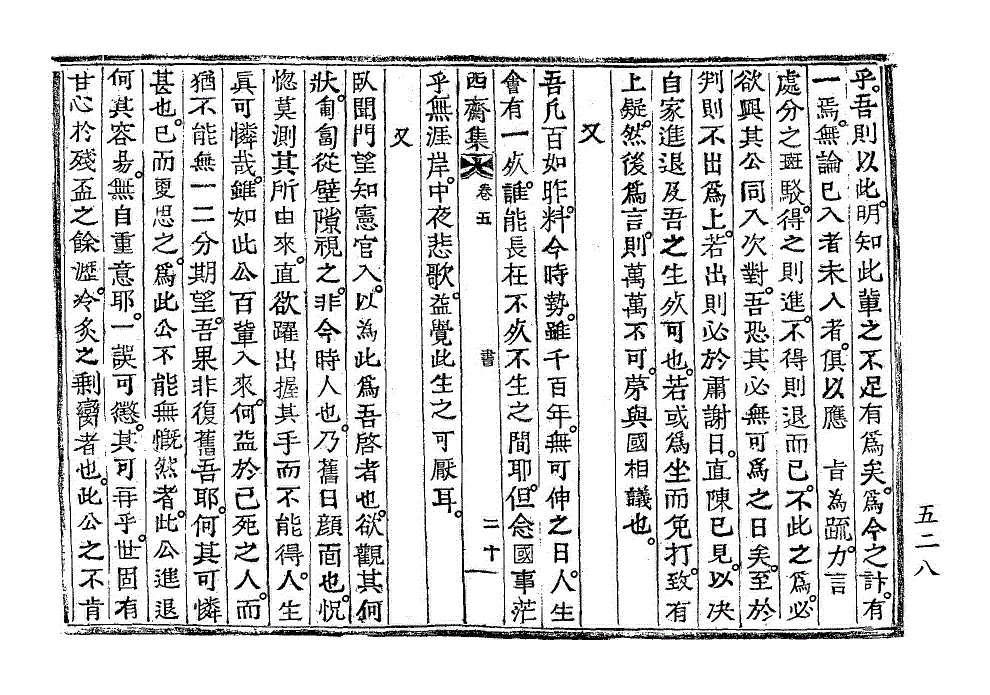 乎。吾则以此。明知此辈之不足有为矣。为今之计。有一焉。无论已入者未入者。俱以应 旨为疏。力言 处分之斑驳。得之则进。不得则退而已。不此之为。必欲与其公同入次对。吾恐其必无可为之日矣。至于判则不出为上。若出则必于肃谢日。直陈己见。以决自家进退及吾之生死可也。若或为坐而免打。致有上疑。然后为言。则万万不可。第与国相议也。
乎。吾则以此。明知此辈之不足有为矣。为今之计。有一焉。无论已入者未入者。俱以应 旨为疏。力言 处分之斑驳。得之则进。不得则退而已。不此之为。必欲与其公同入次对。吾恐其必无可为之日矣。至于判则不出为上。若出则必于肃谢日。直陈己见。以决自家进退及吾之生死可也。若或为坐而免打。致有上疑。然后为言。则万万不可。第与国相议也。寄诸子
吾凡百如昨。料今时势。虽千百年。无可伸之日。人生会有一死。谁能长在不死不生之间耶。但念国事茫乎无涯岸。中夜悲歌。益觉此生之可厌耳。
寄诸子
卧闻门望知宪官入。以为此为吾启者也。欲观其何状。匍匐从壁隙视之。非今时人也。乃旧日颜面也。恍惚莫测其所由来。直欲跃出握其手而不能得。人生真可怜哉。虽如此公百辈入来。何益于已死之人。而犹不能无一二分期望。吾果非复旧吾耶。何其可怜甚也。已而更思之。为此公不能无慨然者。此公进退何其容易。无自重意耶。一误可惩。其可再乎。世固有甘心于残杯之馀沥。冷炙之剩脔者也。此公之不肯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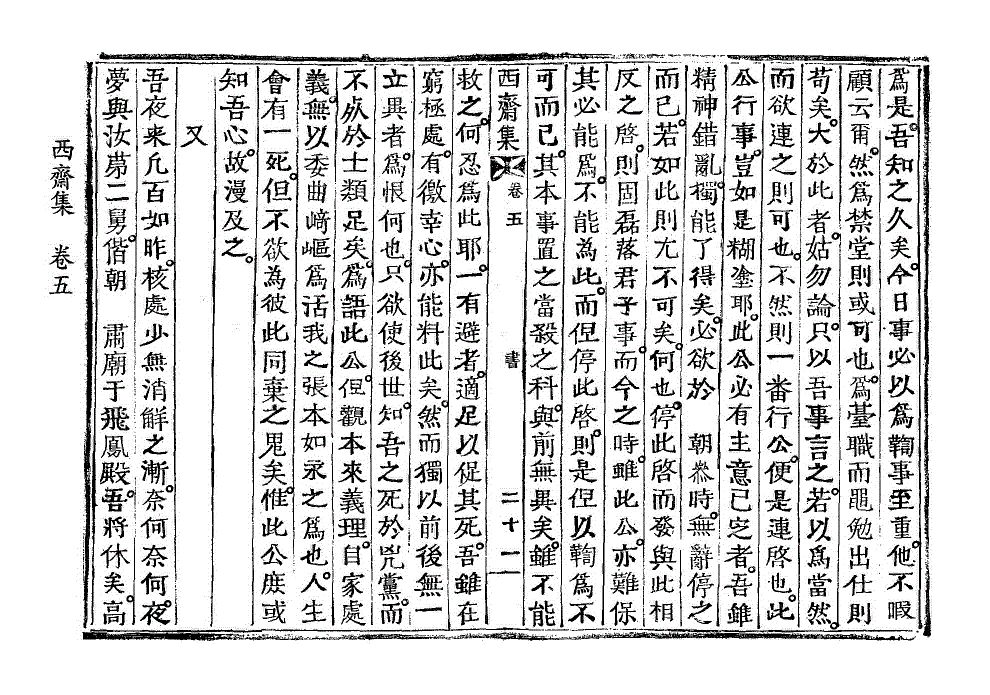 为是。吾知之久矣。今日事必以为鞫事至重。他不暇顾云尔。然为禁堂则或可也。为台职而黾勉出仕则苟矣。大于此者。姑勿论。只以吾事言之。若以为当然。而欲连之则可也。不然则一番行公。便是连启也。此公行事。岂如是糊涂耶。此公必有主意已定者。吾虽精神错乱。独能了得矣。必欲于 朝参时。无辞停之而已。若如此则尤不可矣。何也。停此启而发与此相反之启。则固磊落君子事。而今之时。虽此公。亦难保其必能为。不能为此。而但停此启。则是但以鞫为不可而已。其本事置之当杀之科。与前无异矣。虽不能救之。何忍为此耶。一有避者。适足以促其死。吾虽在穷极处。有徼幸心。亦能料此矣。然而独以前后无一立异者。为恨何也。只欲使后世。知吾之死于凶党。而不死于士类足矣。为语此公。但观本来义理。自家处义。无以委曲崎岖为活我之张本如永之为也。人生会有一死。但不欲为彼此同弃之鬼矣。惟此公庶或知吾心。故漫及之。
为是。吾知之久矣。今日事必以为鞫事至重。他不暇顾云尔。然为禁堂则或可也。为台职而黾勉出仕则苟矣。大于此者。姑勿论。只以吾事言之。若以为当然。而欲连之则可也。不然则一番行公。便是连启也。此公行事。岂如是糊涂耶。此公必有主意已定者。吾虽精神错乱。独能了得矣。必欲于 朝参时。无辞停之而已。若如此则尤不可矣。何也。停此启而发与此相反之启。则固磊落君子事。而今之时。虽此公。亦难保其必能为。不能为此。而但停此启。则是但以鞫为不可而已。其本事置之当杀之科。与前无异矣。虽不能救之。何忍为此耶。一有避者。适足以促其死。吾虽在穷极处。有徼幸心。亦能料此矣。然而独以前后无一立异者。为恨何也。只欲使后世。知吾之死于凶党。而不死于士类足矣。为语此公。但观本来义理。自家处义。无以委曲崎岖为活我之张本如永之为也。人生会有一死。但不欲为彼此同弃之鬼矣。惟此公庶或知吾心。故漫及之。寄诸子
吾夜来凡百如昨。核处少无消解之渐。奈何奈何。夜梦与汝第二舅。偕朝 肃庙于飞凤殿。吾将休矣。高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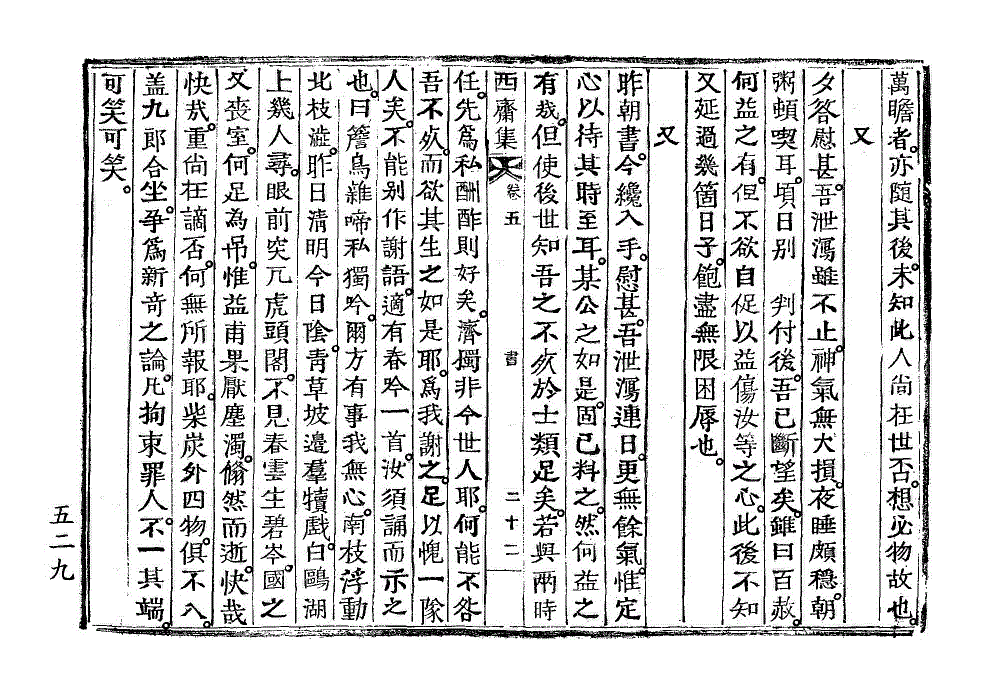 万瞻者。亦随其后。未知此人尚在世否。想必物故也。
万瞻者。亦随其后。未知此人尚在世否。想必物故也。寄诸子
夕答慰甚。吾泄泻虽不止。神气无大损。夜睡颇稳。朝粥顿吃耳。顷日别 判付后。吾已断望矣。虽曰百赦。何益之有。但不欲自促以益伤汝等之心。此后不知又延过几个日子。饱尽无限困辱也。
寄诸子
昨朝书。今才入手。慰甚。吾泄泻连日。更无馀气。惟定心以待其时至耳。某公之如是。固已料之。然何益之有哉。但使后世知吾之不死于士类足矣。若与两时任。先为私酬酢则好矣。济独非今世人耶。何能不咎吾不死。而欲其生之如是耶。为我谢之。足以愧一队人矣。不能别作谢语。适有春吟一首。汝须诵而示之也。曰檐鸟杂啼私独吟。尔方有事我无心。南枝浮动北枝涩。昨日清明今日阴。青草坡边群犊戏。白鸥湖上几人寻。眼前突兀虎头阁。不见春云生碧岑。国之又丧室。何足为吊。惟益甫果厌尘浊。翛然而逝。快哉快哉。重尚在谪否。何无所报耶。柴炭外四物。俱不入。盖九郎合坐。争为新奇之论。凡拘束罪人。不一其端。可笑可笑。
寄诸子
梦有人遗以虎子。其大如拳。张须瞋目。奋爪人立。威风凛然。余曰。此物虽小。已有可畏之威。其性虽恶。姑无已见之害。杀之不祥。盍放诸野。其人抱去良久。为众所劝。终椎杀之。余欲救之。已无及矣。南冥有诗曰人之爱人才。爱虎皮相似。生前欲杀之。死后方称美。此梦无不近于此乎。何其与余今日事相类也。或者养虎必遗患而今除之。可谓除后患乎。异哉异哉。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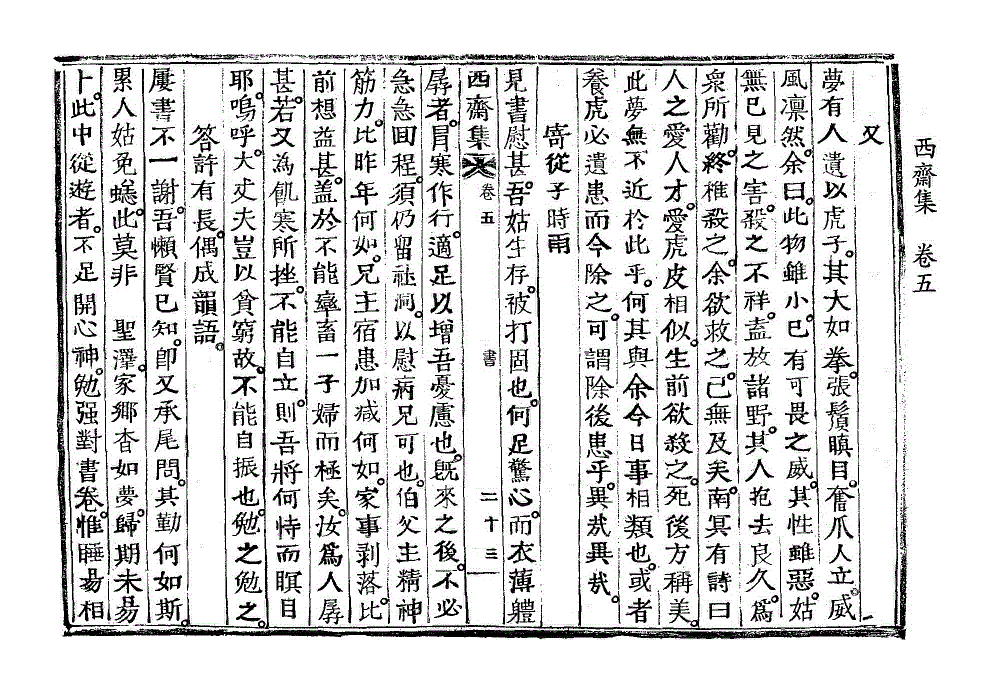 寄从子时雨
寄从子时雨见书慰甚。吾姑生存。被打固也。何足惊心。而衣薄体孱者。冒寒作行。适足以增吾忧虑也。既来之后。不必急急回程。须仍留社洞。以慰病兄可也。伯父主精神筋力。比昨年何如。兄主宿患加减何如。家事剥落。比前想益甚。盖于不能率畜一子妇而极矣。汝为人孱甚。若又为饥寒所挫。不能自立。则吾将何恃而瞑目耶。呜呼。大丈夫岂以贫穷故。不能自振也。勉之勉之。
答许有长。偶成韵语。
屡书不一谢。吾懒贤已知。即又承尾问。其勤何如斯。累人姑免𧏮。此莫非 圣泽。家乡杳如梦。归期未易卜。此中从游者。不足开心神。勉强对书卷。惟睡易相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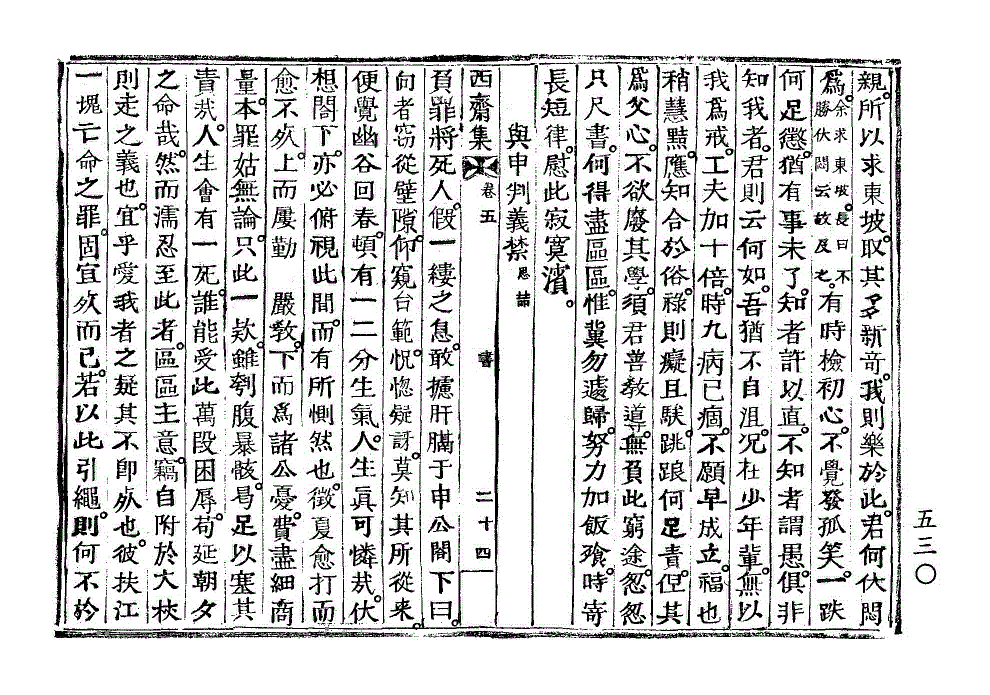 亲。所以求东坡。取其多新奇。我则乐于此。君何伏闷为。(余求东坡。长曰不胜伏闷云故及之。)有时检初心。不觉发孤笑。一跌何足惩。犹有事未了。知者许以直。不知者谓愚。俱非知我者。君则云何如。吾犹不自沮。况在少年辈。无以我为戒。工夫加十倍。时九病已痼。不愿早成立。福也稍慧黠。应知合于俗。禄则痴且騃。跳踉何足责。但其为父心。不欲废其学。须君善教导。无负此穷途。匆匆只尺书。何得尽区区。惟冀勿遽归。努力加饭飧。时寄长短律。慰此寂寞滨。
亲。所以求东坡。取其多新奇。我则乐于此。君何伏闷为。(余求东坡。长曰不胜伏闷云故及之。)有时检初心。不觉发孤笑。一跌何足惩。犹有事未了。知者许以直。不知者谓愚。俱非知我者。君则云何如。吾犹不自沮。况在少年辈。无以我为戒。工夫加十倍。时九病已痼。不愿早成立。福也稍慧黠。应知合于俗。禄则痴且騃。跳踉何足责。但其为父心。不欲废其学。须君善教导。无负此穷途。匆匆只尺书。何得尽区区。惟冀勿遽归。努力加饭飧。时寄长短律。慰此寂寞滨。与申判义禁(思哲)
负罪将死人。假一缕之息。敢摅肝膈于申公閤下曰。向者窃从壁隙。仰窥台范。恍惚疑讶。莫知其所从来。便觉幽谷回春。顿有一二分生气。人生真可怜哉。伏想閤下。亦必俯视此间。而有所恻然也。徵夏愈打而愈不死。上而屡勤 严教。下而为诸公忧。费尽细商量。本罪姑无论。只此一款。虽刳腹暴骸。曷足以塞其责哉。人生会有一死。谁能受此万段困辱。苟延朝夕之命哉。然而濡忍至此者。区区主意。窃自附于大杖则走之义也。宜乎爱我者之疑其不即死也。彼扶江一块亡命之罪。固宜死而已。若以此引绳。则何不于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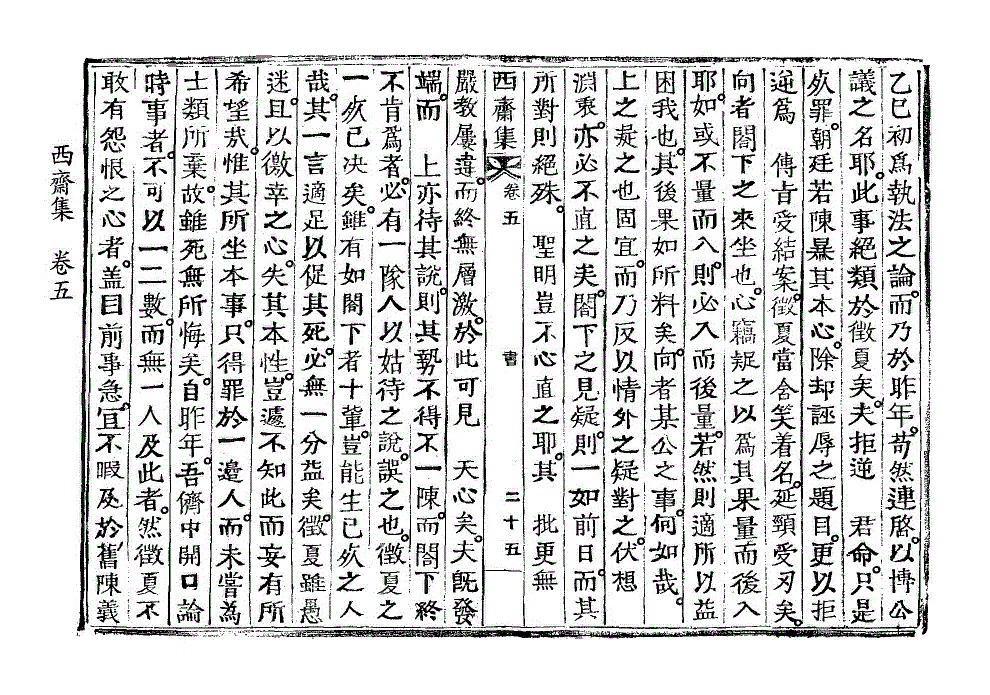 乙巳初为执法之论。而乃于昨年。苟然连启。以博公议之名耶。此事绝类于徵夏矣。夫拒逆 君命。只是死罪。朝廷若陈暴其本心。除却诬辱之题目。更以拒逆为 传旨受结案。徵夏当含笑着名。延颈受刃矣。向者閤下之来坐也。心窃疑之以为其果量而后入耶。如或不量而入。则必入而后量。若然则适所以益困我也。其后果如所料矣。向者某公之事。何如哉。 上之疑之也固宜。而乃反以情外之疑对之。伏想 渊衷。亦必不直之矣。閤下之见疑。则一如前日。而其所对则绝殊。 圣明岂不心直之耶。其 批更无 严教屡违。而终无层激。于此可见 天心矣。夫既发端。而 上亦待其说。则其势不得不一陈。而閤下终不肯为者。必有一队人以姑待之说。误之也。徵夏之一死已决矣。虽有如閤下者十辈。岂能生已死之人哉。其一言适足以促其死。必无一分益矣。徵夏虽愚迷。且以徼幸之心。失其本性。岂遽不知此而妄有所希望哉。惟其所坐本事。只得罪于一边人。而未尝为士类所弃。故虽死无所悔矣。自昨年。吾侪中开口论时事者。不可以一二数。而无一人及此者。然徵夏不敢有怨恨之心者。盖目前事急。宜不暇及于旧陈义
乙巳初为执法之论。而乃于昨年。苟然连启。以博公议之名耶。此事绝类于徵夏矣。夫拒逆 君命。只是死罪。朝廷若陈暴其本心。除却诬辱之题目。更以拒逆为 传旨受结案。徵夏当含笑着名。延颈受刃矣。向者閤下之来坐也。心窃疑之以为其果量而后入耶。如或不量而入。则必入而后量。若然则适所以益困我也。其后果如所料矣。向者某公之事。何如哉。 上之疑之也固宜。而乃反以情外之疑对之。伏想 渊衷。亦必不直之矣。閤下之见疑。则一如前日。而其所对则绝殊。 圣明岂不心直之耶。其 批更无 严教屡违。而终无层激。于此可见 天心矣。夫既发端。而 上亦待其说。则其势不得不一陈。而閤下终不肯为者。必有一队人以姑待之说。误之也。徵夏之一死已决矣。虽有如閤下者十辈。岂能生已死之人哉。其一言适足以促其死。必无一分益矣。徵夏虽愚迷。且以徼幸之心。失其本性。岂遽不知此而妄有所希望哉。惟其所坐本事。只得罪于一边人。而未尝为士类所弃。故虽死无所悔矣。自昨年。吾侪中开口论时事者。不可以一二数。而无一人及此者。然徵夏不敢有怨恨之心者。盖目前事急。宜不暇及于旧陈义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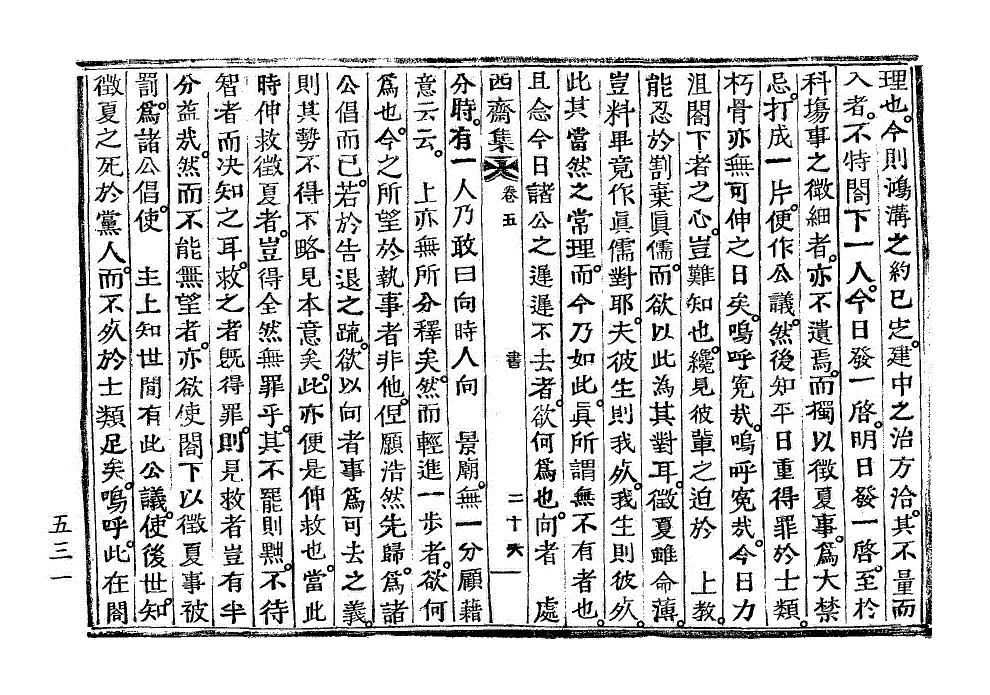 理也。今则鸿沟之约已定。建中之治方洽。其不量而入者。不特閤下一人。今日发一启。明日发一启。至于科场事之微细者。亦不遗焉。而独以徵夏事。为大禁忌。打成一片。便作公议。然后知平日重得罪于士类。朽骨亦无可伸之日矣。呜呼冤哉。呜呼冤哉。今日力沮閤下者之心。岂难知也。才见彼辈之迫于 上教。能忍于割弃真儒。而欲以此为其对耳。徵夏虽命薄。岂料毕竟作真儒对耶。夫彼生则我死。我生则彼死。此其当然之常理。而今乃如此。真所谓无不有者也。且念今日诸公之迟迟不去者。欲何为也。向者 处分时。有一人乃敢曰向时人向 景庙。无一分顾藉意云云。 上亦无所分释矣。然而轻进一步者。欲何为也。今之所望于执事者非他。但愿浩然先归。为诸公倡而已。若于告退之疏。欲以向者事为可去之义。则其势不得不略见本意矣。此亦便是伸救也。当此时伸救徵夏者。岂得全然无罪乎。其不罢则黜。不待智者而决知之耳。救之者既得罪。则见救者岂有半分益哉。然而不能无望者。亦欲使閤下以徵夏事被罚。为诸公倡。使 主上知世间有此公议。使后世。知徵夏之死于党人。而不死于士类足矣。呜呼。此在閤
理也。今则鸿沟之约已定。建中之治方洽。其不量而入者。不特閤下一人。今日发一启。明日发一启。至于科场事之微细者。亦不遗焉。而独以徵夏事。为大禁忌。打成一片。便作公议。然后知平日重得罪于士类。朽骨亦无可伸之日矣。呜呼冤哉。呜呼冤哉。今日力沮閤下者之心。岂难知也。才见彼辈之迫于 上教。能忍于割弃真儒。而欲以此为其对耳。徵夏虽命薄。岂料毕竟作真儒对耶。夫彼生则我死。我生则彼死。此其当然之常理。而今乃如此。真所谓无不有者也。且念今日诸公之迟迟不去者。欲何为也。向者 处分时。有一人乃敢曰向时人向 景庙。无一分顾藉意云云。 上亦无所分释矣。然而轻进一步者。欲何为也。今之所望于执事者非他。但愿浩然先归。为诸公倡而已。若于告退之疏。欲以向者事为可去之义。则其势不得不略见本意矣。此亦便是伸救也。当此时伸救徵夏者。岂得全然无罪乎。其不罢则黜。不待智者而决知之耳。救之者既得罪。则见救者岂有半分益哉。然而不能无望者。亦欲使閤下以徵夏事被罚。为诸公倡。使 主上知世间有此公议。使后世。知徵夏之死于党人。而不死于士类足矣。呜呼。此在閤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2H 页
 下不过拔一毛之损。在徵夏。为百世不泯之资。惟閤下三思而行之。无复与悠悠者谋幸甚。徵夏平日仰恃閤下何如哉。惟閤下故为此言耳。如閤下不以为然。则归朝我 肃考。必有讼辨之事矣。
下不过拔一毛之损。在徵夏。为百世不泯之资。惟閤下三思而行之。无复与悠悠者谋幸甚。徵夏平日仰恃閤下何如哉。惟閤下故为此言耳。如閤下不以为然。则归朝我 肃考。必有讼辨之事矣。与或人(疑与李公倚天○戊申二月)
月前为一书。未知几日能传到兄边也。弟今日事。亦已晚矣。本不足动吾心。且念向者不知死于谁手者几人也。今则有罪无罪。惟吾 君命之也。岂不荣且乐乎。但观时人头势。既请用兴阳例。不得则必将为檀也之为。若终不得一陈所欲言。则此其恨当不与骨俱朽矣。受 命后。匆匆为数个文字。付之迷儿。兄若一览。则可知吾本心耳。世之人。每事必巧占隙地于两端之间。一边为爵禄。一边为明哲。吾甚病之。吾之所以至此者。欲以愧此等人耳。然其有能知愧者否。愧亦未易得也。此外何用多言。惟望为 国保重。
西斋集卷之五
记
万松斋记(韩名锡愈)
余谪来于关西之顺安县。有韩君字大来。与其二弟时来,命来者。往来甚熟。盖玆乡之秀也。余尝乘兴访其书斋。韩氏子弟及邻之俊秀。咸在其中。方屈首读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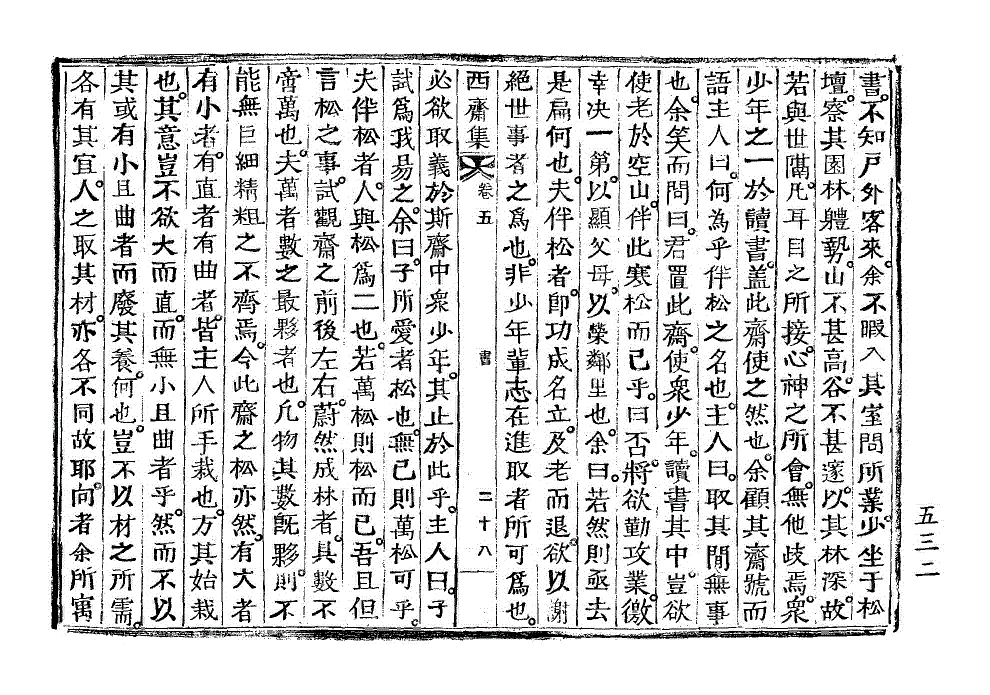 书。不知户外客来。余不暇入其室问所业。少坐于松坛。察其园林体势。山不甚高。谷不甚邃。以其林深。故若与世隔。凡耳目之所接。心神之所会。无他歧焉。众少年之一于读书。盖此斋使之然也。余顾其斋号而语主人曰。何为乎伴松之名也。主人曰。取其閒无事也。余笑而问曰。君置此斋。使众少年。读书其中。岂欲使老于空山。伴此寒松而已乎。曰否。将欲勤攻业。徼幸决一第。以显父母。以荣邻里也。余曰。若然则亟去是扁何也。夫伴松者。即功成名立。及老而退。欲以谢绝世事者之为也。非少年辈志在进取者所可为也。必欲取义于斯斋中众少年。其止于此乎。主人曰。子试为我易之。余曰。子所爱者松也。无已则万松可乎。夫伴松者。人与松为二也。若万松则松而已。吾且但言松之事。试观斋之前后左右。蔚然成林者。具数不啻万也。夫万者数之最夥者也。凡物其数既夥。则不能无巨细精粗之不齐焉。今此斋之松亦然。有大者有小者。有直者有曲者。皆主人所手栽也。方其始栽也。其意岂不欲大而直。而无小且曲者乎。然而不以其或有小且曲者而废其养。何也。岂不以材之所需。各有其宜。人之取其材。亦各不同故耶。向者余所寓
书。不知户外客来。余不暇入其室问所业。少坐于松坛。察其园林体势。山不甚高。谷不甚邃。以其林深。故若与世隔。凡耳目之所接。心神之所会。无他歧焉。众少年之一于读书。盖此斋使之然也。余顾其斋号而语主人曰。何为乎伴松之名也。主人曰。取其閒无事也。余笑而问曰。君置此斋。使众少年。读书其中。岂欲使老于空山。伴此寒松而已乎。曰否。将欲勤攻业。徼幸决一第。以显父母。以荣邻里也。余曰。若然则亟去是扁何也。夫伴松者。即功成名立。及老而退。欲以谢绝世事者之为也。非少年辈志在进取者所可为也。必欲取义于斯斋中众少年。其止于此乎。主人曰。子试为我易之。余曰。子所爱者松也。无已则万松可乎。夫伴松者。人与松为二也。若万松则松而已。吾且但言松之事。试观斋之前后左右。蔚然成林者。具数不啻万也。夫万者数之最夥者也。凡物其数既夥。则不能无巨细精粗之不齐焉。今此斋之松亦然。有大者有小者。有直者有曲者。皆主人所手栽也。方其始栽也。其意岂不欲大而直。而无小且曲者乎。然而不以其或有小且曲者而废其养。何也。岂不以材之所需。各有其宜。人之取其材。亦各不同故耶。向者余所寓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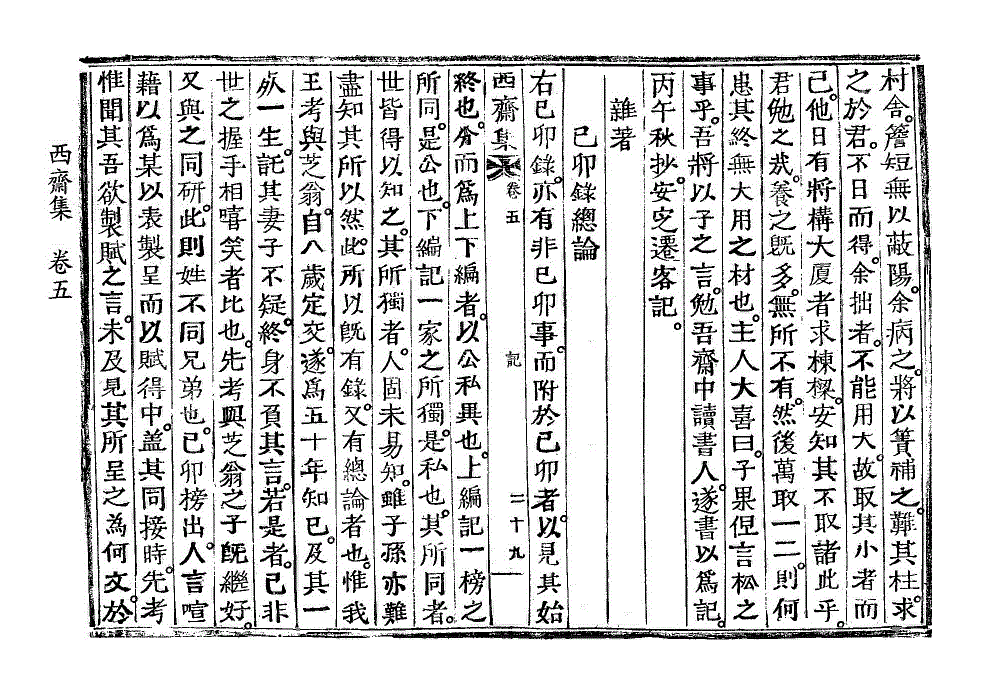 村舍。檐短无以蔽阳。余病之。将以箦补之。难其柱。求之于君。不日而得。余拙者。不能用大。故取其小者而已。他日有将构大厦者求栋梁。安知其不取诸此乎。君勉之哉。养之既多。无所不有。然后万取一二。则何患其终无大用之材也。主人大喜曰。子果但言松之事乎。吾将以子之言。勉吾斋中读书人。遂书以为记。丙午秋杪。安定迁客记。
村舍。檐短无以蔽阳。余病之。将以箦补之。难其柱。求之于君。不日而得。余拙者。不能用大。故取其小者而已。他日有将构大厦者求栋梁。安知其不取诸此乎。君勉之哉。养之既多。无所不有。然后万取一二。则何患其终无大用之材也。主人大喜曰。子果但言松之事乎。吾将以子之言。勉吾斋中读书人。遂书以为记。丙午秋杪。安定迁客记。西斋集卷之五
杂著
己卯录总论
右己卯录。亦有非己卯事。而附于己卯者。以见其始终也。分而为上下编者。以公私异也。上编记一榜之所同。是公也。下编记一家之所独。是私也。其所同者。世皆得以知之。其所独者。人固未易知。虽子孙亦难尽知其所以然。此所以既有录。又有总论者也。惟我王考与芝翁。自八岁定交。遂为五十年知己。及其一死一生。托其妻子不疑。终身不负其言。若是者。已非世之握手相嘻笑者比也。先考与芝翁之子既继好。又与之同研。此则姓不同兄弟也。己卯榜出。人言喧藉以为某以表制呈而以赋得中。盖其同接时。先考惟闻其吾欲制赋之言。未及见其所呈之为何文。于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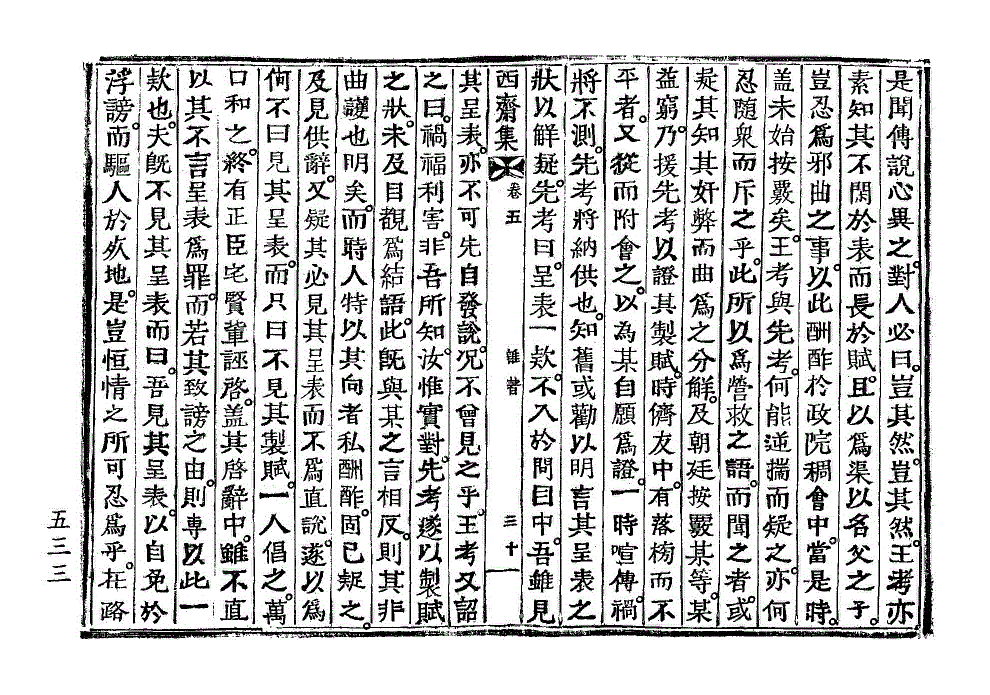 是闻传说心异之。对人必曰。岂其然。岂其然。王考亦素知其不闲于表而长于赋。且以为渠以名父之子。岂忍为邪曲之事。以此酬酢于政院稠会中。当是时。盖未始按覈矣。王考与先考。何能逆揣而疑之。亦何忍随众而斥之乎。此所以为营救之语。而闻之者。或疑其知其奸弊而曲为之分解。及朝廷按覈某等。某益穷。乃援先考以證其制赋。时侪友中。有落榜而不平者。又从而附会之。以为某自愿为證。一时喧传。祸将不测。先考将纳供也。知旧或劝以明言其呈表之状以解疑。先考曰。呈表一款。不入于问目中。吾虽见其呈表。亦不可先自发说。况不曾见之乎。王考又诏之曰。祸福利害。非吾所知。汝惟实对。先考遂以制赋之状。未及目睹为结语。此既与某之言相反。则其非曲护也明矣。而时人特以其向者私酬酢。固已疑之。及见供辞。又疑其必见其呈表而不为直说。遂以为何不曰见其呈表。而只曰不见其制赋。一人倡之。万口和之。终有正臣宅贤辈诬启。盖其启辞中。虽不直以其不言呈表为罪。而若其致谤之由。则专以此一款也。夫既不见其呈表而曰。吾见其呈表。以自免于浮谤。而驱人于死地。是岂恒情之所可忍为乎。在路
是闻传说心异之。对人必曰。岂其然。岂其然。王考亦素知其不闲于表而长于赋。且以为渠以名父之子。岂忍为邪曲之事。以此酬酢于政院稠会中。当是时。盖未始按覈矣。王考与先考。何能逆揣而疑之。亦何忍随众而斥之乎。此所以为营救之语。而闻之者。或疑其知其奸弊而曲为之分解。及朝廷按覈某等。某益穷。乃援先考以證其制赋。时侪友中。有落榜而不平者。又从而附会之。以为某自愿为證。一时喧传。祸将不测。先考将纳供也。知旧或劝以明言其呈表之状以解疑。先考曰。呈表一款。不入于问目中。吾虽见其呈表。亦不可先自发说。况不曾见之乎。王考又诏之曰。祸福利害。非吾所知。汝惟实对。先考遂以制赋之状。未及目睹为结语。此既与某之言相反。则其非曲护也明矣。而时人特以其向者私酬酢。固已疑之。及见供辞。又疑其必见其呈表而不为直说。遂以为何不曰见其呈表。而只曰不见其制赋。一人倡之。万口和之。终有正臣宅贤辈诬启。盖其启辞中。虽不直以其不言呈表为罪。而若其致谤之由。则专以此一款也。夫既不见其呈表而曰。吾见其呈表。以自免于浮谤。而驱人于死地。是岂恒情之所可忍为乎。在路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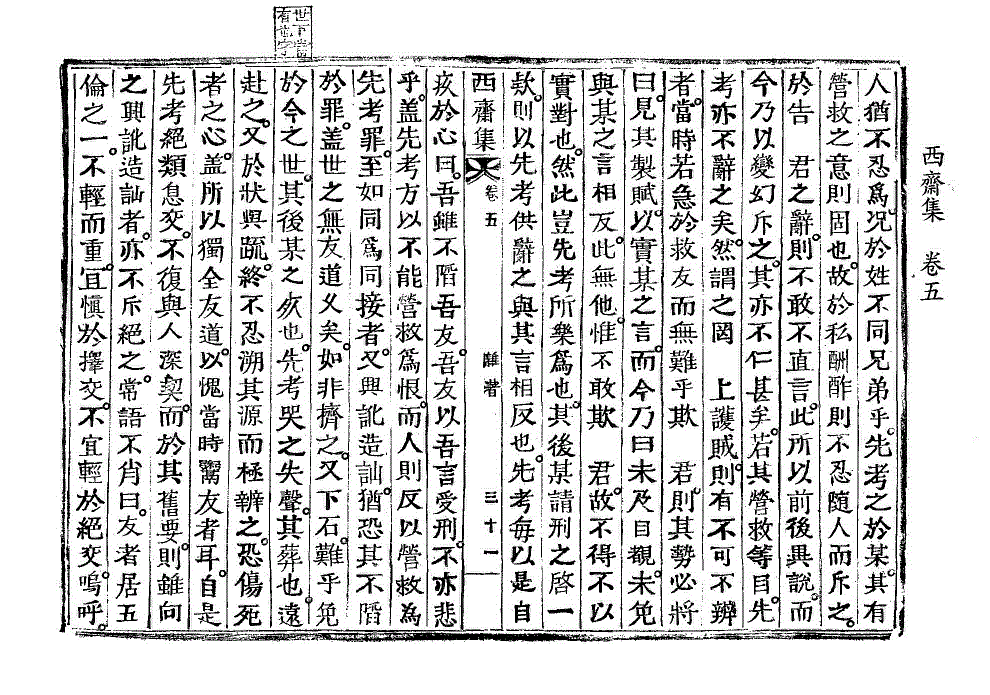 人犹不忍为。况于姓不同兄弟乎。先考之于某。其有营救之意则固也。故于私酬酢则不忍随人而斥之。于告 君之辞。则不敢不直言。此所以前后异说。而今乃以变幻斥之。其亦不仁甚矣。若其营救等目。先考亦不辞之矣。然谓之罔 上护贼。则有不可不辨者。当时若急于救友而无难乎欺 君。则其势必将曰。见其制赋。以实某之言。而今乃曰未及目睹。未免与某之言相反。此无他。惟不敢欺 君。故不得不以实对也。然此岂先考所乐为也。其后某请刑之启一款。则以先考供辞之与其言相反也。先考每以是自疚于心曰。吾虽不陷吾友。吾友以吾言受刑。不亦悲乎。盖先考方以不能营救为恨。而人则反以营救为先考罪。至如同为同接者。又兴讹造讪。犹恐其不陷于罪。盖世之无友道久矣。如非挤之。又下石。难乎免于今之世(世下当有也字)。其后某之死也。先考哭之失声。其葬也。远赴之。又于状与疏。终不忍溯其源而极辨之。恐伤死者之心。盖所以独全友道。以愧当时鬻友者耳。自是先考绝类息交。不复与人深契。而于其旧要。则虽向之兴讹造讪者。亦不斥绝之。常语不肖曰。友者居五伦之一。不轻而重。宜慎于择交。不宜轻于绝交。呜呼。
人犹不忍为。况于姓不同兄弟乎。先考之于某。其有营救之意则固也。故于私酬酢则不忍随人而斥之。于告 君之辞。则不敢不直言。此所以前后异说。而今乃以变幻斥之。其亦不仁甚矣。若其营救等目。先考亦不辞之矣。然谓之罔 上护贼。则有不可不辨者。当时若急于救友而无难乎欺 君。则其势必将曰。见其制赋。以实某之言。而今乃曰未及目睹。未免与某之言相反。此无他。惟不敢欺 君。故不得不以实对也。然此岂先考所乐为也。其后某请刑之启一款。则以先考供辞之与其言相反也。先考每以是自疚于心曰。吾虽不陷吾友。吾友以吾言受刑。不亦悲乎。盖先考方以不能营救为恨。而人则反以营救为先考罪。至如同为同接者。又兴讹造讪。犹恐其不陷于罪。盖世之无友道久矣。如非挤之。又下石。难乎免于今之世(世下当有也字)。其后某之死也。先考哭之失声。其葬也。远赴之。又于状与疏。终不忍溯其源而极辨之。恐伤死者之心。盖所以独全友道。以愧当时鬻友者耳。自是先考绝类息交。不复与人深契。而于其旧要。则虽向之兴讹造讪者。亦不斥绝之。常语不肖曰。友者居五伦之一。不轻而重。宜慎于择交。不宜轻于绝交。呜呼。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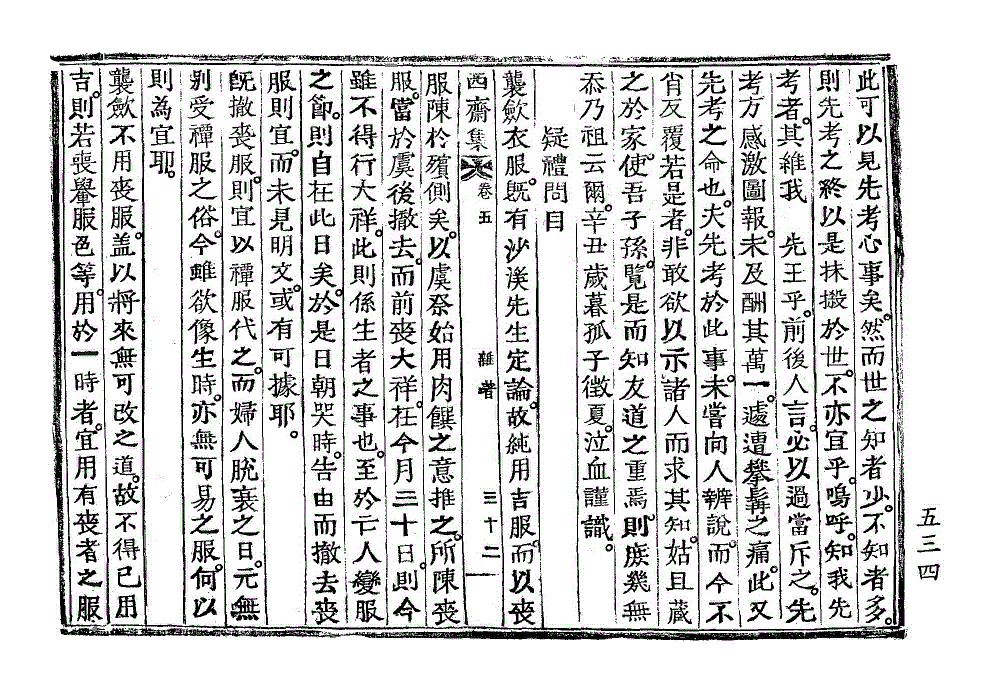 此可以见先考心事矣。然而世之知者少。不知者多。则先考之终以是抹摋于世。不亦宜乎。呜呼。知我先考者。其维我 先王乎。前后人言。必以过当斥之。先考方感激图报。未及酬其万一。遽遭攀髯之痛。此又先考之命也。夫先考于此事。未尝向人辨说。而今不肖反覆若是者。非敢欲以示诸人而求其知。姑且藏之于家。使吾子孙。览是而知友道之重焉。则庶几无忝乃祖云尔。辛丑岁暮孤子徵夏。泣血谨识。
此可以见先考心事矣。然而世之知者少。不知者多。则先考之终以是抹摋于世。不亦宜乎。呜呼。知我先考者。其维我 先王乎。前后人言。必以过当斥之。先考方感激图报。未及酬其万一。遽遭攀髯之痛。此又先考之命也。夫先考于此事。未尝向人辨说。而今不肖反覆若是者。非敢欲以示诸人而求其知。姑且藏之于家。使吾子孙。览是而知友道之重焉。则庶几无忝乃祖云尔。辛丑岁暮孤子徵夏。泣血谨识。疑礼问目
袭敛衣服。既有沙溪先生定论。故纯用吉服。而以丧服陈于殡侧矣。以虞祭始用肉馔之意推之。所陈丧服。当于虞后撤去。而前丧大祥。在今月三十日。则今虽不得行大祥。此则系生者之事也。至于亡人变服之节。则自在此日矣。于是日朝哭时。告由而撤去丧服则宜。而未见明文。或有可据耶。
既撤丧服。则宜以禫服代之。而妇人脱衰之日。元无别受禫服之俗。今虽欲像生时。亦无可易之服。何以则为宜耶。
袭敛不用丧服。盖以将来无可改之道。故不得已用吉。则若丧舆服色等。用于一时者。宜用有丧者之服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5H 页
 色。而不可用华彩决矣。但此发靷。将在于祥月之后。禫月之前。则不可纯华。亦不可纯素。若以淡青布。为盖帷等饰。以示半凶半吉之仪似可。未知如何。
色。而不可用华彩决矣。但此发靷。将在于祥月之后。禫月之前。则不可纯华。亦不可纯素。若以淡青布。为盖帷等饰。以示半凶半吉之仪似可。未知如何。后丧既殡后。行前丧馈奠。明有可据。而至于朔望殷奠。虽是奠也。视朝夕奠。则不可比而同之矣。今此丧家。未及详考讲定。已于月朔。如前设行。此果不当行而行者耶。如有可据明文。以为不可行。则从今改之。亦未为不可耶。
前丧上食。宜用素馔。而孤哀兄弟。荒迷中不能致思。泛用肉馔矣。及考慎斋先生答人问后。始觉其误。欲为改正。则既用肉馔多日之后。今乃无端改以素馔。终涉未安。如不改之。则既知其误而仍之。亦非诚信之道。何以则得宜耶。
葬前。不可行大祥。既有明文矣。但再期忌日。不忍虚度。孤哀兄弟。欲以义起略设。而行之一献而无祝。未知果无悖于礼意否。杂记所谓葬而后祭下注。以其祭字。但释为小祥大祥之祭。后贤亦多论之。而曾无及于忌祭。盖以忌祭。比之练祥则差轻故也。虽然。终是祭也。非奠也。则不可以葬前仍行朝夕奠馈为例。而并与忌祭而不废。今欲略设者。终为未安耶。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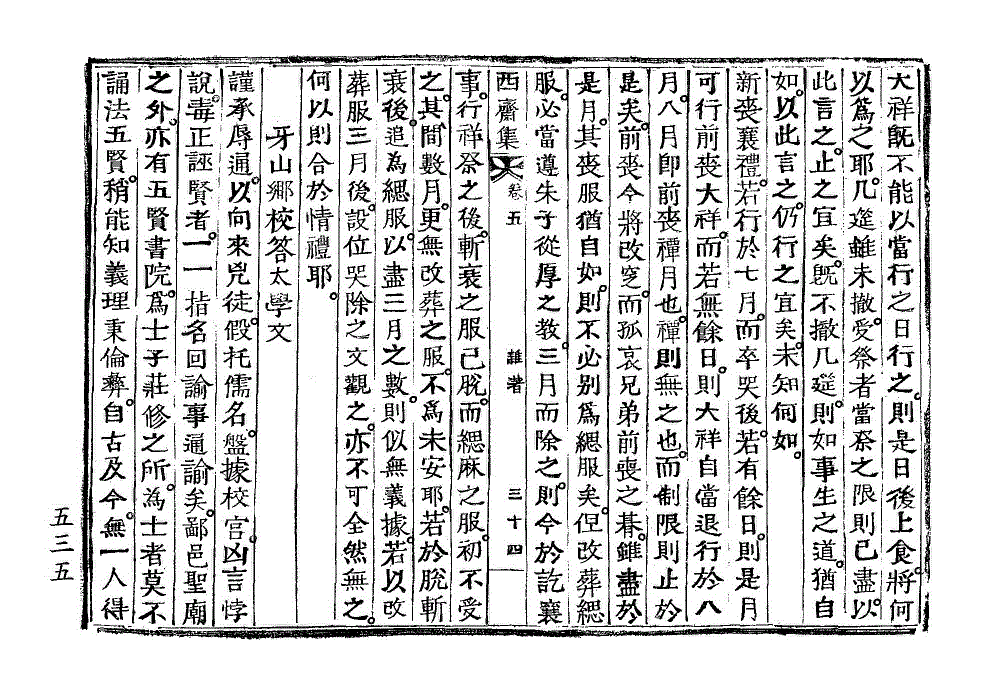 大祥既不能以当行之日行之。则是日后上食。将何以为之耶。几筵虽未撤。受祭者当祭之限则已尽。以此言之。止之宜矣。既不撤几筵。则如事生之道。犹自如。以此言之。仍行之宜矣。未知何如。
大祥既不能以当行之日行之。则是日后上食。将何以为之耶。几筵虽未撤。受祭者当祭之限则已尽。以此言之。止之宜矣。既不撤几筵。则如事生之道。犹自如。以此言之。仍行之宜矣。未知何如。新丧襄礼。若行于七月。而卒哭后。若有馀日。则是月可行前丧大祥。而若无馀日。则大祥自当退行于八月。八月即前丧禫月也。禫则无之也。而制限则止于是矣。前丧今将改窆。而孤哀兄弟前丧之期。虽尽于是月。其丧服犹自如。则不必别为缌服矣。但改葬缌服。必当遵朱子从厚之教。三月而除之。则今于讫襄事。行祥祭之后。斩衰之服已脱。而缌麻之服。初不受之。其间数月。更无改葬之服。不为未安耶。若于脱斩衰后。追为缌服。以尽三月之数。则似无义据。若以改葬服三月后。设位哭除之文观之。亦不可全然无之。何以则合于情礼耶。
牙山乡校答太学文
谨承辱通。以向来凶徒。假托儒名。盘据校宫。凶言悖说。毒正诬贤者。一一指名回谕事通谕矣。鄙邑圣庙之外。亦有五贤书院。为士子庄修之所。为士者莫不诵法五贤。稍能知义理秉伦彝。自古及今。无一人得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6H 页
 罪于伦义。为羞于士林者。不幸凶歙出。而举一邑之士子。无可显之面目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呜呼。人心日益陷溺。义理日益晦塞。如歙之贰于 圣母。斁败伦彝者。其势益张。甚于洪水之滔天。其为 圣母严讨复。以明义理于千万世。得蒙嘉奖于 圣考。如慷慨翁者。终死于士祸。而歙疏实为之祟。此则中外远近之所共愤。况我一邑之士。孰不钦仰慷慨翁之气节。而仇视凶歙。羞与之同邑哉。盖自庚子以后。歙之徒自以为得其秋。一乡之无识凡民。曾欲厕迹于儒林而不可得者。并起而应募。列名于凶疏。终乃以儒籍。为酬功之资。于是所谓儒籍无异于军案矣。当此时。鄙等既不能鸣鼓而攻之。以明其非吾徒。则不如我谨避之而已。由是为士者迹不到儒宫已五年矣。彼之䲭张豕突。直以不治治之。盖其相与讲定者如是矣。目今皓天既复。 新化清明。凶贼之头颅已破。士类之正论稍振。以鄙邑言之。慷慨翁已蒙 赠职 赐祭之典。所以明既晦之义理。树方来之风声也。此已如此。则彼戕害慷慨翁者。宜自 朝廷亟行诛讨。鄙等方拭目而待之。然此则 朝廷事也。惟我士林之所以讨罪者。不过削名于儒籍。使不得复肆
罪于伦义。为羞于士林者。不幸凶歙出。而举一邑之士子。无可显之面目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呜呼。人心日益陷溺。义理日益晦塞。如歙之贰于 圣母。斁败伦彝者。其势益张。甚于洪水之滔天。其为 圣母严讨复。以明义理于千万世。得蒙嘉奖于 圣考。如慷慨翁者。终死于士祸。而歙疏实为之祟。此则中外远近之所共愤。况我一邑之士。孰不钦仰慷慨翁之气节。而仇视凶歙。羞与之同邑哉。盖自庚子以后。歙之徒自以为得其秋。一乡之无识凡民。曾欲厕迹于儒林而不可得者。并起而应募。列名于凶疏。终乃以儒籍。为酬功之资。于是所谓儒籍无异于军案矣。当此时。鄙等既不能鸣鼓而攻之。以明其非吾徒。则不如我谨避之而已。由是为士者迹不到儒宫已五年矣。彼之䲭张豕突。直以不治治之。盖其相与讲定者如是矣。目今皓天既复。 新化清明。凶贼之头颅已破。士类之正论稍振。以鄙邑言之。慷慨翁已蒙 赠职 赐祭之典。所以明既晦之义理。树方来之风声也。此已如此。则彼戕害慷慨翁者。宜自 朝廷亟行诛讨。鄙等方拭目而待之。然此则 朝廷事也。惟我士林之所以讨罪者。不过削名于儒籍。使不得复肆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6L 页
 其凶而已。谨与一邑之士。齐会于圣庙。凶歙以下参疏人及其间浊乱校宫丑辱善类者。并施永削之罚。而今承来谕。谨复拈出其元恶。数其罪而悉论之。以备佥尊之裁处焉。凶歙疏下中进士金重吕。贱不得齿于儒林。大以是恨。乃率其弟侄。应募参疏。其疏语之至凶极悖姑无论。重吕之庶妹。即慷慨翁之妾也。半生率畜。多生子女。其恩义何如也。而急于附托凶党。不遑念及于伦理。乃挺身主张于请杀妹夫之疏。若是者尚可以人理责之乎。至如歙之叔洪重周。歙之诸弟某某等。相率而入于校宫。便同族会。乃与其所谓斋任辈。倡为凶论。以讨逆榜三字。大书题目。而列书一邑士类之名。总以结之曰。四凶馀党。至于进士辛锡奎名下。则书以虱附逆某。某者即故殉义尹上舍名也。辛即与尹上舍同事者故也。以是一笔勾断。无所持疑。一邑士林之酷被丑辱。虽不足恤。并与四大臣之纯忠。尹上舍之义节。而诬诋之至于此极。呜呼可胜痛哉。可胜痛哉。玆前所论凶徒。不可以本邑儒罚惩其罪。玆敢胪列而仰复。惟愿佥尊。辟之廓如。使凶徒有所少戢焉。窃念有阳则必有阴。天道之常也。是以有君子则必有小人。亦其势固然。所可异
其凶而已。谨与一邑之士。齐会于圣庙。凶歙以下参疏人及其间浊乱校宫丑辱善类者。并施永削之罚。而今承来谕。谨复拈出其元恶。数其罪而悉论之。以备佥尊之裁处焉。凶歙疏下中进士金重吕。贱不得齿于儒林。大以是恨。乃率其弟侄。应募参疏。其疏语之至凶极悖姑无论。重吕之庶妹。即慷慨翁之妾也。半生率畜。多生子女。其恩义何如也。而急于附托凶党。不遑念及于伦理。乃挺身主张于请杀妹夫之疏。若是者尚可以人理责之乎。至如歙之叔洪重周。歙之诸弟某某等。相率而入于校宫。便同族会。乃与其所谓斋任辈。倡为凶论。以讨逆榜三字。大书题目。而列书一邑士类之名。总以结之曰。四凶馀党。至于进士辛锡奎名下。则书以虱附逆某。某者即故殉义尹上舍名也。辛即与尹上舍同事者故也。以是一笔勾断。无所持疑。一邑士林之酷被丑辱。虽不足恤。并与四大臣之纯忠。尹上舍之义节。而诬诋之至于此极。呜呼可胜痛哉。可胜痛哉。玆前所论凶徒。不可以本邑儒罚惩其罪。玆敢胪列而仰复。惟愿佥尊。辟之廓如。使凶徒有所少戢焉。窃念有阳则必有阴。天道之常也。是以有君子则必有小人。亦其势固然。所可异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7H 页
 者。鄙邑一小县也。既生慷慨翁。以一个布衣。能扶亘天地不泯之纲常。而又生妖慝凶悖如歙,重吕者。为其对头。使一邑之士。一以为荣。一以为羞。岂天故生如歙者。以成就翁之名也欤。此又为士者之不可不知也。玆并及之。惟冀照谅。
者。鄙邑一小县也。既生慷慨翁。以一个布衣。能扶亘天地不泯之纲常。而又生妖慝凶悖如歙,重吕者。为其对头。使一邑之士。一以为荣。一以为羞。岂天故生如歙者。以成就翁之名也欤。此又为士者之不可不知也。玆并及之。惟冀照谅。平壤太学谕列邑儒生文
右通谕。为积愤竭诚。合辞齐声。请讨乱贼。冀正伦纲者。窃惟乱臣贼子。人得而诛之。此千古不易之正案也。夫诛有罪。是王者之事也。今人人而诛之者。岂非以乱贼之罪。不容于天地。讨复之义。无间于贵贱故欤。夫既人人云尔。则虽舆儓马卒。无不可焉。况士者为四民之首。其所业。非农工商三者之比也。幼而学修齐治平之道。壮而欲行。则迹虽草野。其志未尝不在 朝廷。若曰 朝廷事何与于我。是岂知义理。能无愧于士之名者哉。又况我 朝以士气为国家元气。三百年来。 朝廷有大事。为士者辄得以论之。非一二也。今于人人得而诛之之乱贼。而不思所以诛之。是岂人乎哉。呜呼。乱臣贼子。何代无之。未有如辛壬凶党之最可恶。而不可一刻容贷者也。试撮其大者言之。泰耇首发嫌字。以为吾 君之祸根。缔合宦
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7L 页
 寺。终售北门之凶计。凤辉指斥 储位。无异劾正。上诬 慈圣。不少顾藉。恒佐主张诬狱。欲以上及。至如疏下五贼。只是五个镜贼而已。其他固结妖俭。图为不轨。阴助逆镜。坐观成败。观其形迹。虽有缓急之殊。论其心肠。罔非叛逆之类。此而不讨。其于三百年 宗社何。其于千万世讥议何。然而 主上过于恭谦。不遑惩讨。廷臣安于姑息。无人担当。上下因循。遂至于今若此而已。则 宗社之贼。何时可讨。 君父之雠。何时可复。目今三年之制已讫。一初之政方新。此正 君臣上下奋发大志。廓清氛埃。以迓天命。以定民志之秋也。仄听踰月。一如前日。此岂特肉食者之羞哉。藿食者亦与有其责焉。鄙等为是之惧。谨与一邑之章甫。约以某月某日。会议本邑乡校。某月某日。封章登途。愿随诸君子后。讨今日谋害吾 君者。凡我一道之士。孰无同仇之意。惟愿佥尊。深究义理。激起忠愤。父诏其子。兄教其弟。大邑五六人。小邑三四人。以原定日。齐会于弊邑。毋以一二人塞责。毋以疏资钱代纳。如或无一人来者。来而或后于期者。举邑停举。自有常典。勖哉无忽焉。仍窃念今此讨逆一事。实神人之所共愤。而中外之所同请者。而惟我关西
寺。终售北门之凶计。凤辉指斥 储位。无异劾正。上诬 慈圣。不少顾藉。恒佐主张诬狱。欲以上及。至如疏下五贼。只是五个镜贼而已。其他固结妖俭。图为不轨。阴助逆镜。坐观成败。观其形迹。虽有缓急之殊。论其心肠。罔非叛逆之类。此而不讨。其于三百年 宗社何。其于千万世讥议何。然而 主上过于恭谦。不遑惩讨。廷臣安于姑息。无人担当。上下因循。遂至于今若此而已。则 宗社之贼。何时可讨。 君父之雠。何时可复。目今三年之制已讫。一初之政方新。此正 君臣上下奋发大志。廓清氛埃。以迓天命。以定民志之秋也。仄听踰月。一如前日。此岂特肉食者之羞哉。藿食者亦与有其责焉。鄙等为是之惧。谨与一邑之章甫。约以某月某日。会议本邑乡校。某月某日。封章登途。愿随诸君子后。讨今日谋害吾 君者。凡我一道之士。孰无同仇之意。惟愿佥尊。深究义理。激起忠愤。父诏其子。兄教其弟。大邑五六人。小邑三四人。以原定日。齐会于弊邑。毋以一二人塞责。毋以疏资钱代纳。如或无一人来者。来而或后于期者。举邑停举。自有常典。勖哉无忽焉。仍窃念今此讨逆一事。实神人之所共愤。而中外之所同请者。而惟我关西西斋集卷之五 第 5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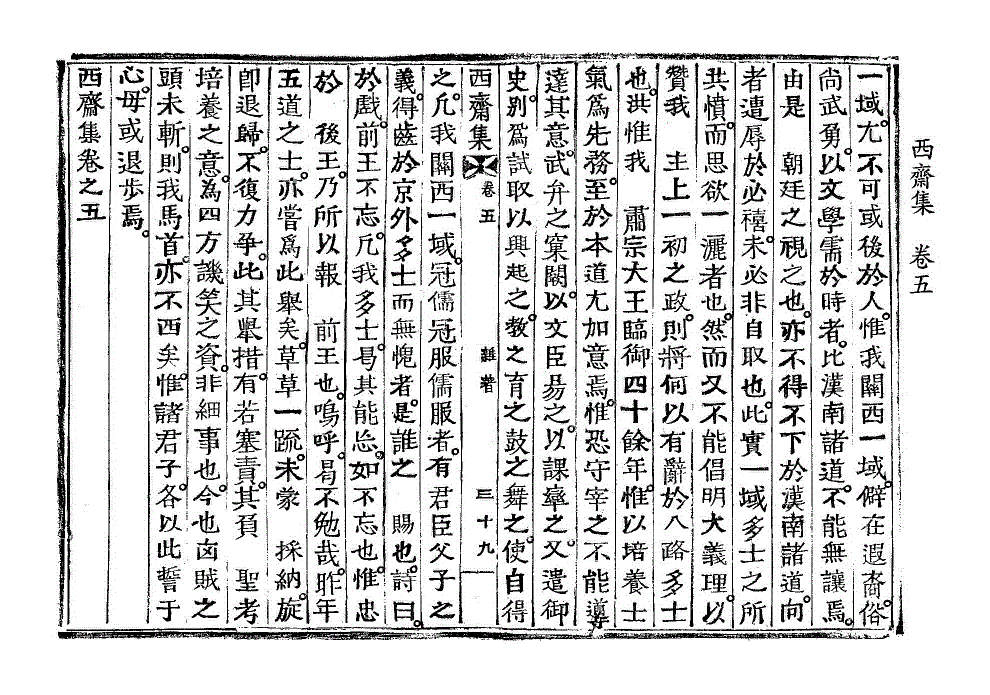 一域。尤不可或后于人。惟我关西一域。僻在遐裔。俗尚武勇。以文学需于时者。比汉南诸道。不能无让焉。由是 朝廷之视之也。亦不得不下于汉南诸道。向者遭辱于必禧。未必非自取也。此实一域多士之所共愤。而思欲一洒者也。然而又不能倡明大义理。以赞我 主上一初之政。则将何以有辞于八路多士也。洪惟我 肃宗大王临御四十馀年。惟以培养士气为先务。至于本道尤加意焉。惟恐守宰之不能导达其意。武弁之窠阙。以文臣易之。以课率之。又遣御史。别为试取以兴起之。教之育之鼓之舞之。使自得之。凡我关西一域。冠儒冠服儒服者。有君臣父子之义。得齿于京外多士而无愧者。是谁之 赐也。诗曰。于戏。前王不忘。凡我多士。曷其能忘。如不忘也。惟忠于 后王。乃所以报 前王也。呜呼。曷不勉哉。昨年五道之士。亦尝为此举矣。草草一疏。未蒙 采纳。旋即退归。不复力争。此其举措。有若塞责。其负 圣考培养之意。为四方讥笑之资。非细事也。今也凶贼之头未斩。则我马首。亦不西矣。惟诸君子。各以此誓于心。毋或退步焉。
一域。尤不可或后于人。惟我关西一域。僻在遐裔。俗尚武勇。以文学需于时者。比汉南诸道。不能无让焉。由是 朝廷之视之也。亦不得不下于汉南诸道。向者遭辱于必禧。未必非自取也。此实一域多士之所共愤。而思欲一洒者也。然而又不能倡明大义理。以赞我 主上一初之政。则将何以有辞于八路多士也。洪惟我 肃宗大王临御四十馀年。惟以培养士气为先务。至于本道尤加意焉。惟恐守宰之不能导达其意。武弁之窠阙。以文臣易之。以课率之。又遣御史。别为试取以兴起之。教之育之鼓之舞之。使自得之。凡我关西一域。冠儒冠服儒服者。有君臣父子之义。得齿于京外多士而无愧者。是谁之 赐也。诗曰。于戏。前王不忘。凡我多士。曷其能忘。如不忘也。惟忠于 后王。乃所以报 前王也。呜呼。曷不勉哉。昨年五道之士。亦尝为此举矣。草草一疏。未蒙 采纳。旋即退归。不复力争。此其举措。有若塞责。其负 圣考培养之意。为四方讥笑之资。非细事也。今也凶贼之头未斩。则我马首。亦不西矣。惟诸君子。各以此誓于心。毋或退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