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x 页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青松斋辨录[上]
青松斋辨录[上]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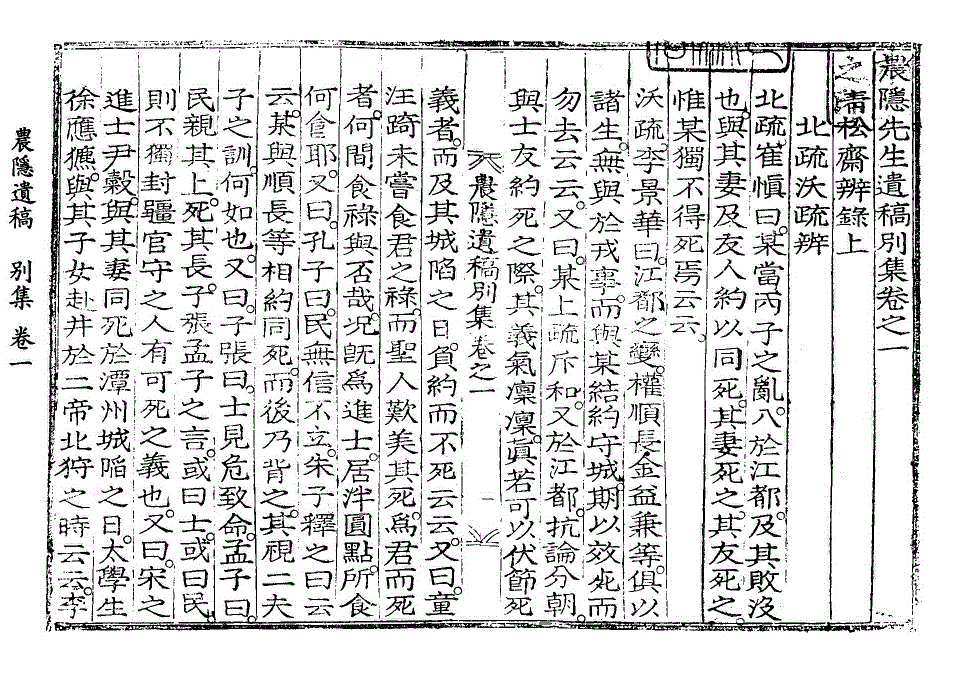 北疏沃疏辨
北疏沃疏辨北疏。崔慎曰。某当丙子之乱。入于江都。及其败没也。与其妻及友人约以同死。其妻死之。其友死之。惟某独不得死焉云云。
沃疏。李景华曰。江都之变。权顺长,金益兼等。俱以诸生。无与于戎事。而与某结约守城。期以效死而勿去云云。又曰。某上疏斥和。又于江都。抗论分朝。与士友约死之际。其义气凛凛。真若可以伏节死义者。而及其城陷之日。负约而不死云云。又曰。童汪踦未尝食君之禄。而圣人叹美其死。为君而死者。何间食禄与否哉。况既为进士。居泮圆点。所食何食耶。又曰。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朱子释之曰云云。某与顺长等相约同死。而后乃背之。其视二夫子之训。何如也。又曰。子张曰。士见危致命。孟子曰。民亲其上。死其长。子张孟子之言。或曰士。或曰民。则不独封疆官守之人有可死之义也。又曰。宋之进士尹谷。与其妻同死于潭州城陷之日。太学生徐应𤣄。与其子女赴井于二帝北狩之时云云。李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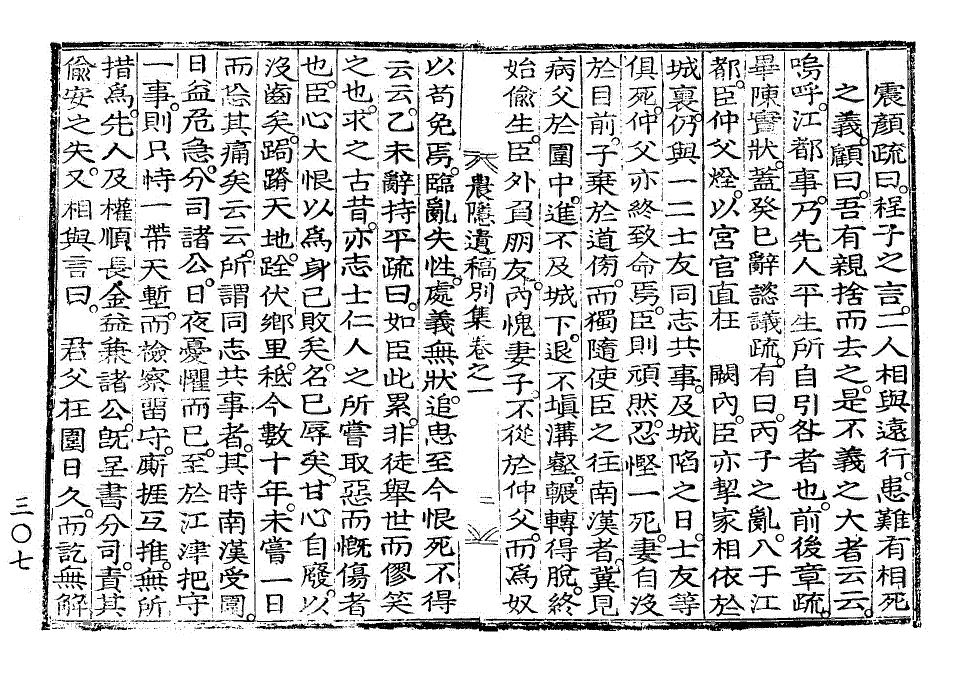 震颜疏曰。程子之言。二人相与远行。患难有相死之义。顾曰。吾有亲舍而去之。是不义之大者云云。
震颜疏曰。程子之言。二人相与远行。患难有相死之义。顾曰。吾有亲舍而去之。是不义之大者云云。呜呼。江都事。乃先人平生所自引咎者也。前后章疏。毕陈实状。盖癸巳辞𧫎议疏。有曰。丙子之乱。入于江都。臣仲父烇。以宫官直在 阙内。臣亦挈家。相依于城里。仍与一二士友同志共事。及城陷之日。士友等俱死。仲父亦终致命焉。臣则顽然。忍悭一死。妻自没于目前。子弃于道傍。而独随使臣之往南汉者。冀见病父于围中。进不及城下。退不填沟壑。辗转得脱。终始偷生。臣外负朋友。内愧妻子。不从于仲父。而为奴以苟免焉。临乱失性。处义无状。追思至今恨死不得云云。乙未辞持平疏曰。如臣此累。非徒举世而僇笑之也。求之古昔。亦志士仁人之所尝取恶而慨伤者也。臣心大恨以为身已败矣。名已辱矣。甘心自废。以没齿矣。跼蹐天地。跧伏乡里。秪今数十年。未尝一日而忘其痛矣云云。所谓同志共事者。其时南汉受围。日益危急。分司诸公。日夜忧惧而已。至于江津把守一事。则只恃一带天堑。而检察留守。厮挨互推。无所措为。先人及权顺长,金益兼诸公。既呈书分司。责其偷安之失。又相与言曰。 君父在围日久。而讫无解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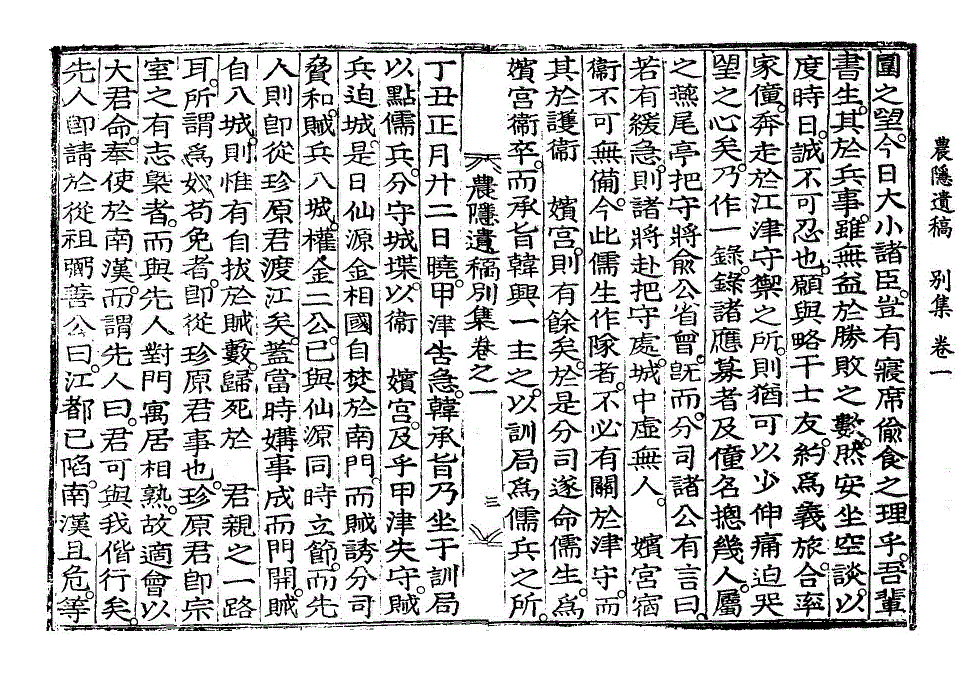 围之望。今日大小诸臣。岂有寝席偷食之理乎。吾辈书生。其于兵事。虽无益于胜败之数。然安坐空谈。以度时日。诚不可忍也。愿与略干士友。约为义旅。合率家僮。奔走于江津守御之所。则犹可以少伸痛迫哭望之心矣。乃作一录。录诸应募者及僮名总几人。属之燕尾亭把守将俞公省曾。既而。分司诸公有言曰。若有缓急。则诸将赴把守处。城中虚无人。 嫔宫宿卫不可无备。今此儒生作队者。不必有关于津守。而其于护卫 嫔宫。则有馀矣。于是分司遂命儒生。为嫔宫卫卒。而承旨韩兴一主之。以训局为儒兵之所。丁丑正月廿二日晓。甲津告急。韩承旨乃坐于训局以点儒兵。分守城堞。以卫 嫔宫。及乎甲津失守。贼兵迫城。是日仙源金相国自焚于南门。而贼诱分司䝱和。贼兵入城。权金二公。已与仙源同时立节。而先人则即从珍原君渡江矣。盖当时媾事成而门开。贼自入城。则惟有自拔于贼数。归死于 君亲之一路耳。所谓为奴苟免者。即从珍原君事也。珍原君即宗室之有志槩者。而与先人对门寓居相熟。故适会以大君命。奉使于南汉。而谓先人曰。君可与我偕行矣。先人即请于从祖弼善公曰。江都已陷。南汉且危。等
围之望。今日大小诸臣。岂有寝席偷食之理乎。吾辈书生。其于兵事。虽无益于胜败之数。然安坐空谈。以度时日。诚不可忍也。愿与略干士友。约为义旅。合率家僮。奔走于江津守御之所。则犹可以少伸痛迫哭望之心矣。乃作一录。录诸应募者及僮名总几人。属之燕尾亭把守将俞公省曾。既而。分司诸公有言曰。若有缓急。则诸将赴把守处。城中虚无人。 嫔宫宿卫不可无备。今此儒生作队者。不必有关于津守。而其于护卫 嫔宫。则有馀矣。于是分司遂命儒生。为嫔宫卫卒。而承旨韩兴一主之。以训局为儒兵之所。丁丑正月廿二日晓。甲津告急。韩承旨乃坐于训局以点儒兵。分守城堞。以卫 嫔宫。及乎甲津失守。贼兵迫城。是日仙源金相国自焚于南门。而贼诱分司䝱和。贼兵入城。权金二公。已与仙源同时立节。而先人则即从珍原君渡江矣。盖当时媾事成而门开。贼自入城。则惟有自拔于贼数。归死于 君亲之一路耳。所谓为奴苟免者。即从珍原君事也。珍原君即宗室之有志槩者。而与先人对门寓居相熟。故适会以大君命。奉使于南汉。而谓先人曰。君可与我偕行矣。先人即请于从祖弼善公曰。江都已陷。南汉且危。等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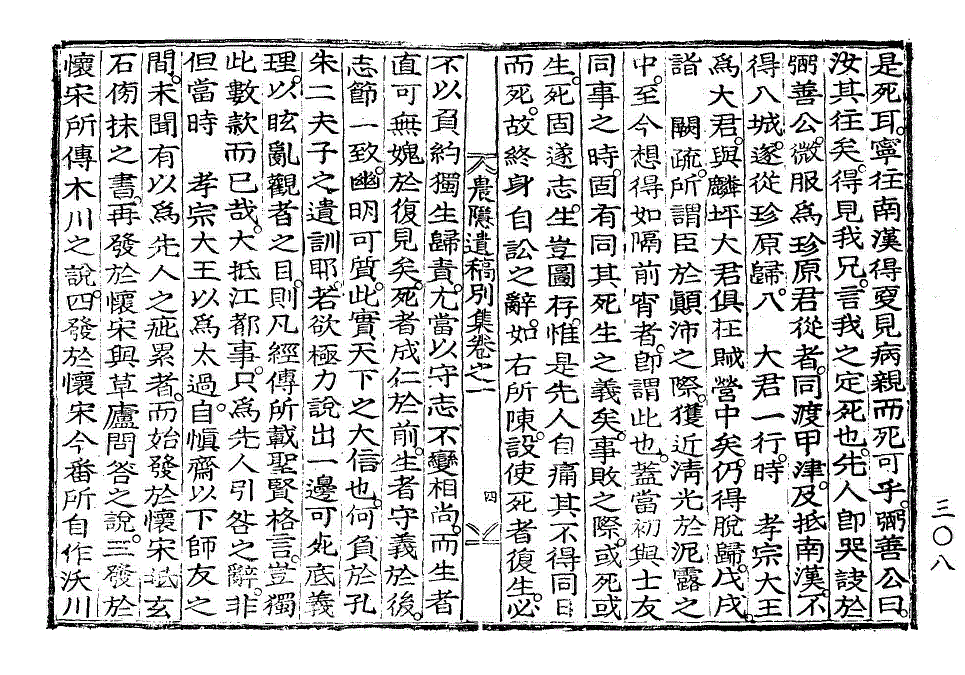 是死耳。宁往南汉得更见病亲而死可乎。弼善公曰。汝其往矣。得见我兄。言我之定死也。先人即哭诀于弼善公。微服为珍原君从者。同渡甲津。及抵南汉。不得入城。遂从珍原归。入 大君一行。时 孝宗大王为大君。与麟坪大君俱在贼营中矣。仍得脱归。戊戌。诣 阙疏。所谓臣于颠沛之际。获近清光于泥露之中。至今想得如隔前宵者。即谓此也。盖当初与士友同事之时。固有同其死生之义矣。事败之际。或死或生。死固遂志。生岂图存。惟是先人自痛其不得同日而死。故终身自讼之辞。如右所陈。设使死者复生。必不以负约独生归责。尤当以守志不变相尚。而生者直可无愧于复见矣。死者成仁于前。生者守义于后。志节一致。幽明可质。此实天下之大信也。何负于孔朱二夫子之遗训耶。若欲极力说出一边可死底义理。以眩乱观者之目。则凡经传所载圣贤格言。岂独此数款而已哉。大抵江都事。只为先人引咎之辞。非但当时 孝宗大王以为太过。自慎斋以下师友之间。未闻有以为先人之疵累者。而始发于怀宋抵玄石傍抹之书。再发于怀宋与草庐问答之说。三发于怀宋所传木川之说。四发于怀宋今番所自作沃川
是死耳。宁往南汉得更见病亲而死可乎。弼善公曰。汝其往矣。得见我兄。言我之定死也。先人即哭诀于弼善公。微服为珍原君从者。同渡甲津。及抵南汉。不得入城。遂从珍原归。入 大君一行。时 孝宗大王为大君。与麟坪大君俱在贼营中矣。仍得脱归。戊戌。诣 阙疏。所谓臣于颠沛之际。获近清光于泥露之中。至今想得如隔前宵者。即谓此也。盖当初与士友同事之时。固有同其死生之义矣。事败之际。或死或生。死固遂志。生岂图存。惟是先人自痛其不得同日而死。故终身自讼之辞。如右所陈。设使死者复生。必不以负约独生归责。尤当以守志不变相尚。而生者直可无愧于复见矣。死者成仁于前。生者守义于后。志节一致。幽明可质。此实天下之大信也。何负于孔朱二夫子之遗训耶。若欲极力说出一边可死底义理。以眩乱观者之目。则凡经传所载圣贤格言。岂独此数款而已哉。大抵江都事。只为先人引咎之辞。非但当时 孝宗大王以为太过。自慎斋以下师友之间。未闻有以为先人之疵累者。而始发于怀宋抵玄石傍抹之书。再发于怀宋与草庐问答之说。三发于怀宋所传木川之说。四发于怀宋今番所自作沃川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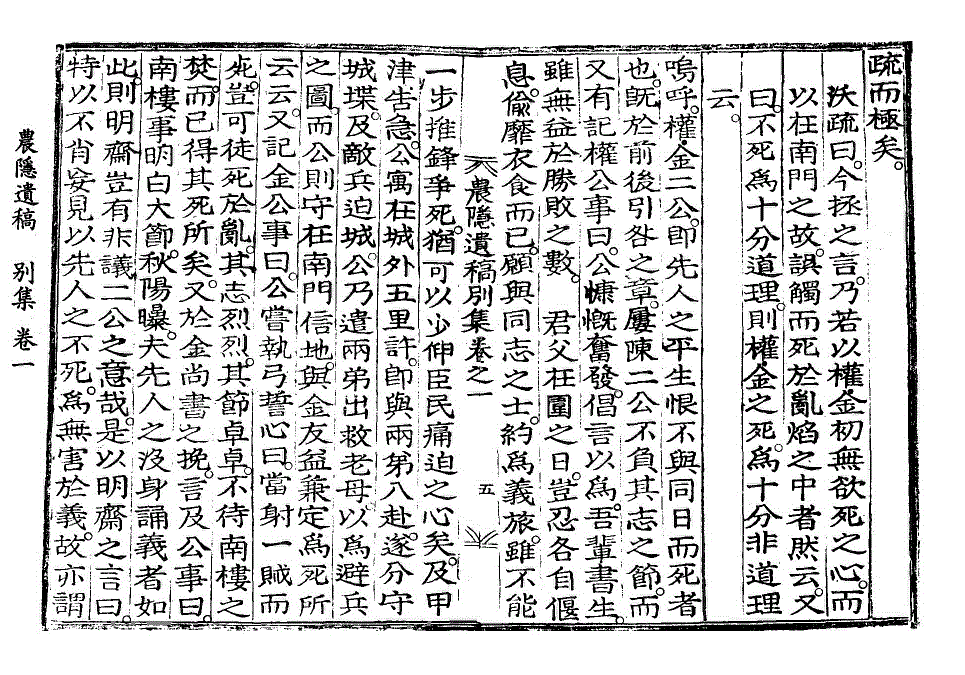 疏而极矣。
疏而极矣。沃疏曰。今拯之言。乃若以权,金初无欲死之心。而以在南门之故。误触而死于乱焰之中者然云。又曰。不死为十分道理。则权,金之死。为十分非道理云。
呜呼。权,金二公。即先人之平生恨不与同日而死者也。既于前后引咎之章。屡陈二公不负其志之节。而又有记权公事曰。公慷慨奋发。倡言以为。吾辈书生。虽无益于胜败之数。 君父在围之日。岂忍各自偃息。偷靡衣食而已。愿与同志之士。约为义旅。虽不能一步推锋争死。犹可以少伸臣民痛迫之心矣。及甲津告急。公寓在城外五里许。即与两弟入赴。遂分守城堞。及敌兵迫城。公乃遣两弟出救老母。以为避兵之图。而公则守在南门信地。与金友益兼定为死所云云。又记金公事曰。公尝执弓誓心曰。当射一贼而死。岂可徒死于乱。其志烈烈。其节卓卓。不待南楼之焚。而已得其死所矣。又于金尚书之挽。言及公事曰。南楼事明白大节。秋阳曝。夫先人之没身诵义者如此。则明斋岂有非议二公之意哉。是以明斋之言曰。特以不肖妄见以先人之不死。为无害于义。故亦谓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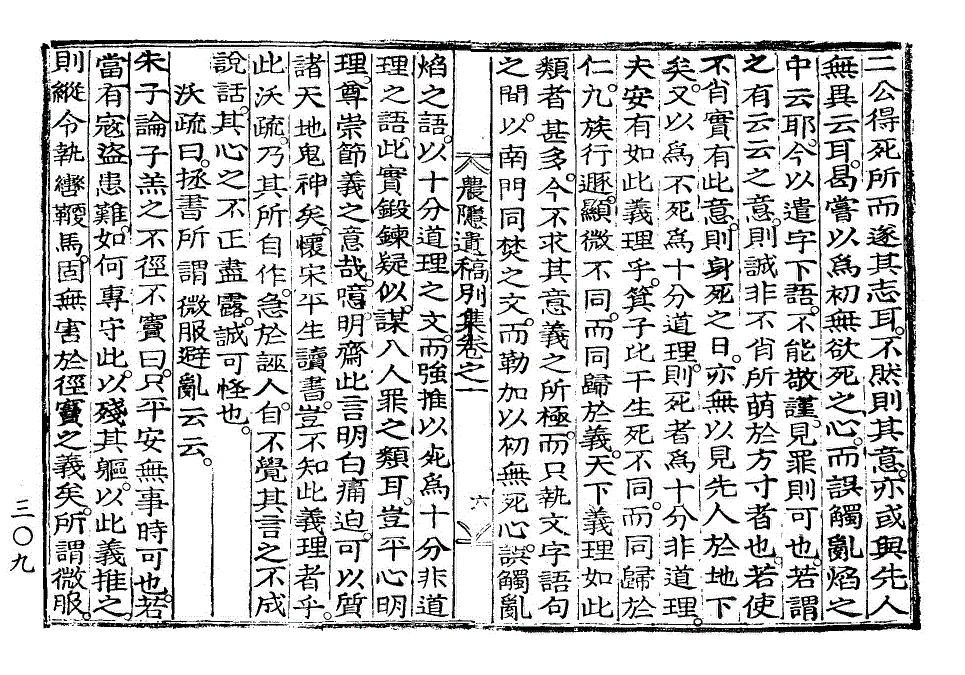 二公得死所而遂其志耳。不然则其意。亦或与先人无异云耳。曷尝以为初无欲死之心。而误触乱焰之中云耶。今以遣字下语。不能敬谨。见罪则可也。若谓之有云云之意。则诚非不肖所萌于方寸者也。若使不肖实有此意。则身死之日。亦无以见先人于地下矣。又以为不死为十分道理。则死者为十分非道理。夫安有如此义理乎。箕子比干生死不同。而同归于仁。九族行遁。显微不同。而同归于义。天下义理如此类者甚多。今不求其意义之所极。而只执文字语句之间。以南门同焚之文。而勒加以初无死心。误触乱焰之语。以十分道理之文。而强推以死为十分非道理之语。此实锻鍊疑似。谋入人罪之类耳。岂平心明理。尊崇节义之意哉。噫。明斋此言明白痛迫。可以质诸天地鬼神矣。怀宋平生读书。岂不知此义理者乎。此沃疏。乃其所自作。急于诬人。自不觉其言之不成说话。其心之不正尽露。诚可怪也。
二公得死所而遂其志耳。不然则其意。亦或与先人无异云耳。曷尝以为初无欲死之心。而误触乱焰之中云耶。今以遣字下语。不能敬谨。见罪则可也。若谓之有云云之意。则诚非不肖所萌于方寸者也。若使不肖实有此意。则身死之日。亦无以见先人于地下矣。又以为不死为十分道理。则死者为十分非道理。夫安有如此义理乎。箕子比干生死不同。而同归于仁。九族行遁。显微不同。而同归于义。天下义理如此类者甚多。今不求其意义之所极。而只执文字语句之间。以南门同焚之文。而勒加以初无死心。误触乱焰之语。以十分道理之文。而强推以死为十分非道理之语。此实锻鍊疑似。谋入人罪之类耳。岂平心明理。尊崇节义之意哉。噫。明斋此言明白痛迫。可以质诸天地鬼神矣。怀宋平生读书。岂不知此义理者乎。此沃疏。乃其所自作。急于诬人。自不觉其言之不成说话。其心之不正尽露。诚可怪也。沃疏曰。拯书所谓微服避乱云云。
朱子论子羔之不径不窦曰。只平安无事时可也。若当有寇盗患难。如何专守此。以残其躯。以此义推之。则纵令执辔鞭马。固无害于径窦之义矣。所谓微服。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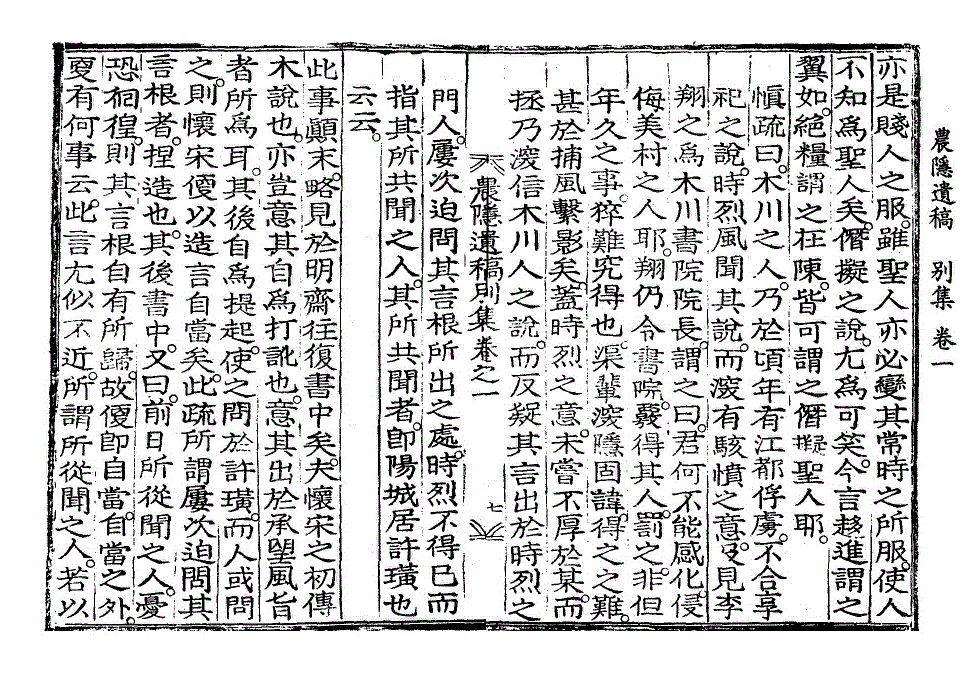 亦是贱人之服。虽圣人亦必变其常时之所服。使人不知为圣人矣。僭拟之说。尤为可笑。今言趍进谓之翼如。绝粮谓之在陈。皆可谓之僭拟圣人耶。
亦是贱人之服。虽圣人亦必变其常时之所服。使人不知为圣人矣。僭拟之说。尤为可笑。今言趍进谓之翼如。绝粮谓之在陈。皆可谓之僭拟圣人耶。慎疏曰。木川之人。乃于顷年有江都俘虏。不合享祀之说。时烈风闻其说。而深有骇愤之意。及见李翔之为木川书院院长。谓之曰。君何不能感化。侵侮美村之人耶。翔仍令书院。覈得其人。罚之。非但年久之事。猝难究得也。渠辈深隐固讳。得之之难。甚于捕风系影矣。盖时烈之意。未尝不厚于某。而拯乃深信木川人之说。而反疑其言出于时烈之门人。屡次迫问其言根所出之处。时烈不得已而指其所共闻之人。其所共闻者。即阳城居许璜也云云。
此事颠末。略见于明斋往复书中矣。夫怀宋之初传木说也。亦岂意其自为打讹也。意其出于承望风旨者所为耳。其后自为提起。使之问于许璜。而人或问之。则怀宋便以造言自当矣。此疏所谓屡次迫问其言根者。捏造也。其后书中。又曰。前日所从闻之人。忧恐徊徨。则其言根自有所归。故便即自当。自当之外。更有何事云。此言尤似不近。所谓所从闻之人。若以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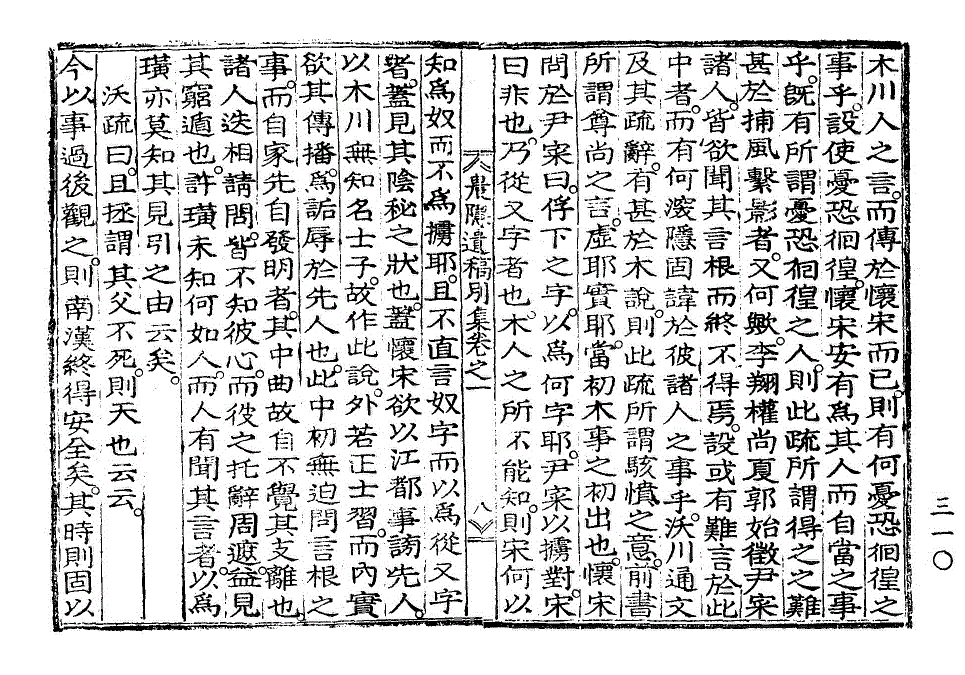 木川人之言。而传于怀宋而已。则有何忧恐徊徨之事乎。设使忧恐徊徨。怀宋安有为其人而自当之事乎。既有所谓忧恐徊徨之人。则此疏所谓得之之难甚于捕风系影者。又何欤。李翔,权尚夏,郭始徵,尹寀诸人。皆欲闻其言根而终不得焉。设或有难言于此中者。而有何深隐固讳于彼诸人之事乎。沃川通文及其疏辞。有甚于木说。则此疏所谓骇愤之意。前书所谓尊尚之言。虚耶实耶。当初木事之初出也。怀宋问于尹寀曰。俘下之字。以为何字耶。尹寀以掳对。宋曰非也。乃从又字者也。木人之所不能知。则宋何以知为奴而不为掳耶。且不直言奴字而以为从又字者。盖见其阴秘之状也。盖怀宋欲以江都事谤先人。以木川无知名士子。故作此说。外若正士习。而内实欲其传播。为诟辱于先人也。此中初无迫问言根之事。而自家先自发明者。其中曲故自不觉其支离也。诸人迭相请问。皆不知彼心。而彼之托辞周遮。益见其穷遁也。许璜未知何如人。而人有闻其言者。以为璜亦莫知其见引之由云矣。
木川人之言。而传于怀宋而已。则有何忧恐徊徨之事乎。设使忧恐徊徨。怀宋安有为其人而自当之事乎。既有所谓忧恐徊徨之人。则此疏所谓得之之难甚于捕风系影者。又何欤。李翔,权尚夏,郭始徵,尹寀诸人。皆欲闻其言根而终不得焉。设或有难言于此中者。而有何深隐固讳于彼诸人之事乎。沃川通文及其疏辞。有甚于木说。则此疏所谓骇愤之意。前书所谓尊尚之言。虚耶实耶。当初木事之初出也。怀宋问于尹寀曰。俘下之字。以为何字耶。尹寀以掳对。宋曰非也。乃从又字者也。木人之所不能知。则宋何以知为奴而不为掳耶。且不直言奴字而以为从又字者。盖见其阴秘之状也。盖怀宋欲以江都事谤先人。以木川无知名士子。故作此说。外若正士习。而内实欲其传播。为诟辱于先人也。此中初无迫问言根之事。而自家先自发明者。其中曲故自不觉其支离也。诸人迭相请问。皆不知彼心。而彼之托辞周遮。益见其穷遁也。许璜未知何如人。而人有闻其言者。以为璜亦莫知其见引之由云矣。沃疏曰。且拯谓其父不死。则天也云云。
今以事过后观之。则南汉终得安全矣。其时则固以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1H 页
 为当如江都之陷败也。岂以为可全之地而为有生之心哉。不图其生而竟免于死。故谓之莫之为之天也。为奴之语。节节提起。以肆诟辱。夫从珍原之行者。只为归死于南汉。岂以求生而为奴耶。
为当如江都之陷败也。岂以为可全之地而为有生之心哉。不图其生而竟免于死。故谓之莫之为之天也。为奴之语。节节提起。以肆诟辱。夫从珍原之行者。只为归死于南汉。岂以求生而为奴耶。沃疏曰。某每以死罪臣自称者云云。
死罪之称。先人丁酉戊戌两疏尽之。违命之本心。固在于江都事。而称以死罪。以违命故耳。两疏俱在。不复多辨。
沃疏曰。既曰不死是十分道理。而又曰痛自刻责。宁有得十分道理。而痛自刻责者乎。又曰以为初无可死之义。则只欲归见老亲同死于南汉者。何意耶。
栗谷之疏。自以入山。为难濯之疵。而上自 朝廷。下至士论。未闻以此为栗谷之疵。先人引咎之疏。亦自以为处义无状。恨死不得。而上自 朝廷。下至诸贤。亦未有以此为先人之疵者。然则不可以自讼之言。定其义理之是非也明矣。江都则虽无必死之义。设使南汉陷败。而 君亲不免。则其无同死之义耶。未知以何言谓之径庭耶。
沃疏曰。洪福以拯为孝子。无所不用其极。又曰其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1L 页
 所言无非不孝之实云云。
所言无非不孝之实云云。明斋之言曰。不肖不孝之罪。何可胜言。碣铭之前。可以知彼心之所存。而矇然无觉。误托不朽。惹起无限唇舌。木事之后。可以知此义之所决。而务欲弥缝。吞吐不得。驯致无限狼狈。以之贻辱先人。贻累世道。不肖不孝之罪。何可胜言。噫。明斋之伤痛悔恨。安得不如此。当初误托。既失于前。而欲其弥缝。亦是苟且之私意。无非可悔可恨。柰何柰何。至于猜嫌之云。彼以忌克之心。自多猜嫌。楚辞曰。内恕己而量人。各兴心而嫉妒。盖以己之心度人。谓人亦有是心也。
沃疏曰。某师事文敬公金集。又曰。拯以珥为时烈之渊源。欲攻时烈。必先攻珥。朱子所谓今日纷纷。不为程氏发者。正谓此也。
此说极为可笑。先贤道统。自有后世公议。岂有自家公然欲揽取属之于己者乎。金文敬先生。实自栗谷沙溪直下相传。栗谷岂独为怀宋之渊源乎。而复引朱子言以證之。不几于侮圣言者乎。
沃疏曰。援引先正臣李珥。以为混并优劣之端。而隐然为吹毛求疵之计。比拟于李珥已极无伦。而况其辞抑扬。反以珥为真有所失。而其父则元无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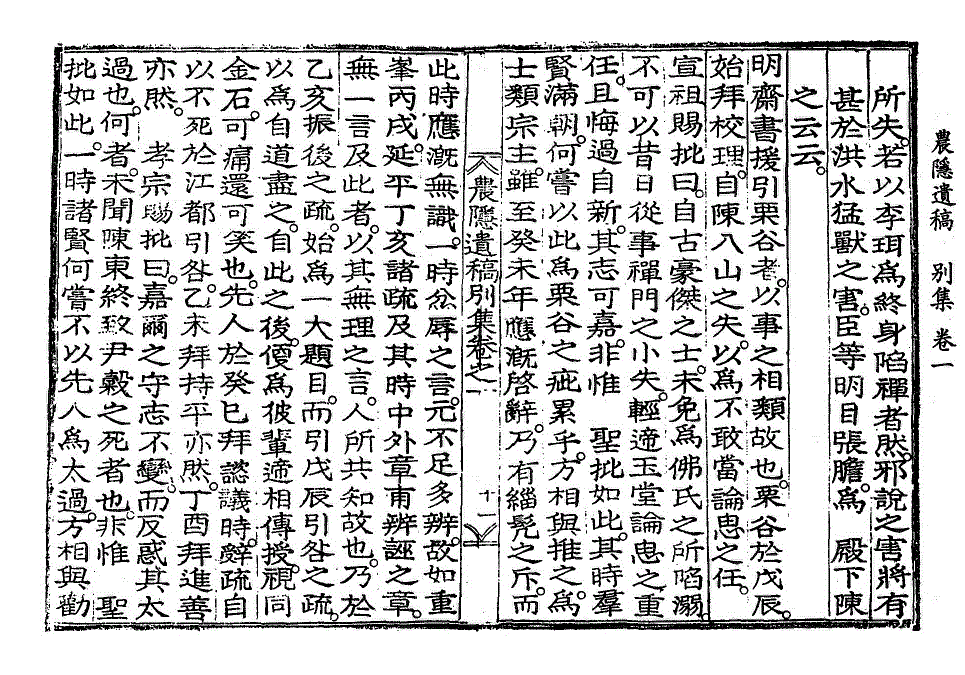 所失。若以李珥为终身陷禅者然。邪说之害将有甚于洪水猛兽之害。臣等明目张胆。为 殿下陈之云云。
所失。若以李珥为终身陷禅者然。邪说之害将有甚于洪水猛兽之害。臣等明目张胆。为 殿下陈之云云。明斋书援引栗谷者。以事之相类故也。栗谷于戊辰始拜校理。自陈入山之失。以为不敢当论思之任。 宣祖赐批曰。自古豪杰之士。未免为佛氏之所陷溺。不可以昔日从事禅门之小失。轻递玉堂论思之重任。且悔过自新。其志可嘉。非惟 圣批如此。其时群贤满朝。何尝以此为栗谷之疵累乎。方相与推之。为士类宗主。虽至癸未年应溉启辞。乃有缁髡之斥。而此时应溉无识。一时忿辱之言。元不足多辨。故如重峰丙戌。延平丁亥诸疏及其时中外章甫辨诬之章。无一言及此者。以其无理之言。人所共知故也。乃于乙亥振后之疏。始为一大题目。而引戊辰引咎之疏。以为自道尽之。自此之后。便为彼辈递相传授。视同金石。可痛还可笑也。先人于癸巳拜𧫎议时。辞疏自以不死于江都引咎。乙未拜持平亦然。丁酉拜进善亦然。 孝宗赐批曰。嘉尔之守志不变。而反惑其太过也。何者。未闻陈东终致尹谷之死者也。非惟 圣批如此。一时诸贤何尝不以先人为太过。方相与劝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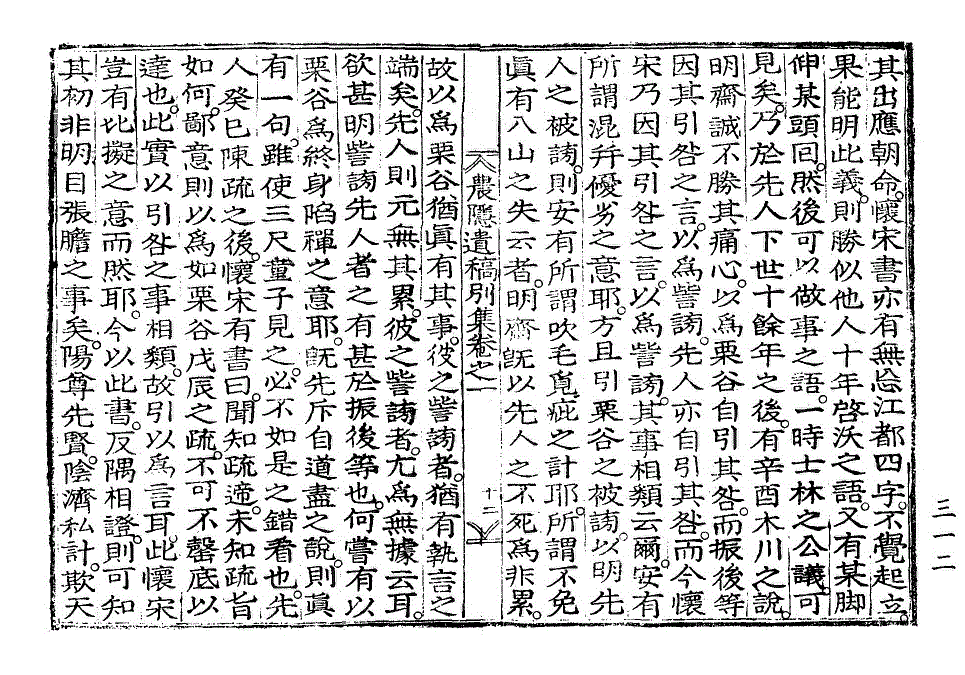 其出应朝命。怀宋书亦有无忘江都四字。不觉起立。果能明此义。则胜似他人十年启沃之语。又有某脚伸某头回。然后可以做事之语。一时士林之公议。可见矣。乃于先人下世十馀年之后。有辛酉木川之说。明斋诚不胜其痛心。以为栗谷自引其咎。而振后等因其引咎之言。以为訾谤。先人亦自引其咎。而今怀宋乃因其引咎之言。以为訾谤。其事相类云尔。安有所谓混并优劣之意耶。方且引栗谷之被谤。以明先人之被谤。则安有所谓吹毛觅疵之计耶。所谓不免真有入山之失云者。明斋既以先人之不死为非累。故以为栗谷犹真有其事。彼之訾谤者。犹有执言之端矣。先人则元无其累。彼之訾谤者。尤为无据云耳。欲甚明訾谤先人者之有甚于振后等也。何尝有以栗谷为终身陷禅之意耶。既先斥自道尽之说。则真有一句。虽使三尺童子见之。必不如是之错看也。先人癸巳陈疏之后。怀宋有书曰。闻知疏递。未知疏旨如何。鄙意则以为如栗谷戊辰之疏。不可不罄底以达也。此实以引咎之事相类。故引以为言耳。此怀宋岂有比拟之意而然耶。今以此书。反隅相證。则可知其初非明目张胆之事矣。阳尊先贤。阴济私计。欺天
其出应朝命。怀宋书亦有无忘江都四字。不觉起立。果能明此义。则胜似他人十年启沃之语。又有某脚伸某头回。然后可以做事之语。一时士林之公议。可见矣。乃于先人下世十馀年之后。有辛酉木川之说。明斋诚不胜其痛心。以为栗谷自引其咎。而振后等因其引咎之言。以为訾谤。先人亦自引其咎。而今怀宋乃因其引咎之言。以为訾谤。其事相类云尔。安有所谓混并优劣之意耶。方且引栗谷之被谤。以明先人之被谤。则安有所谓吹毛觅疵之计耶。所谓不免真有入山之失云者。明斋既以先人之不死为非累。故以为栗谷犹真有其事。彼之訾谤者。犹有执言之端矣。先人则元无其累。彼之訾谤者。尤为无据云耳。欲甚明訾谤先人者之有甚于振后等也。何尝有以栗谷为终身陷禅之意耶。既先斥自道尽之说。则真有一句。虽使三尺童子见之。必不如是之错看也。先人癸巳陈疏之后。怀宋有书曰。闻知疏递。未知疏旨如何。鄙意则以为如栗谷戊辰之疏。不可不罄底以达也。此实以引咎之事相类。故引以为言耳。此怀宋岂有比拟之意而然耶。今以此书。反隅相證。则可知其初非明目张胆之事矣。阳尊先贤。阴济私计。欺天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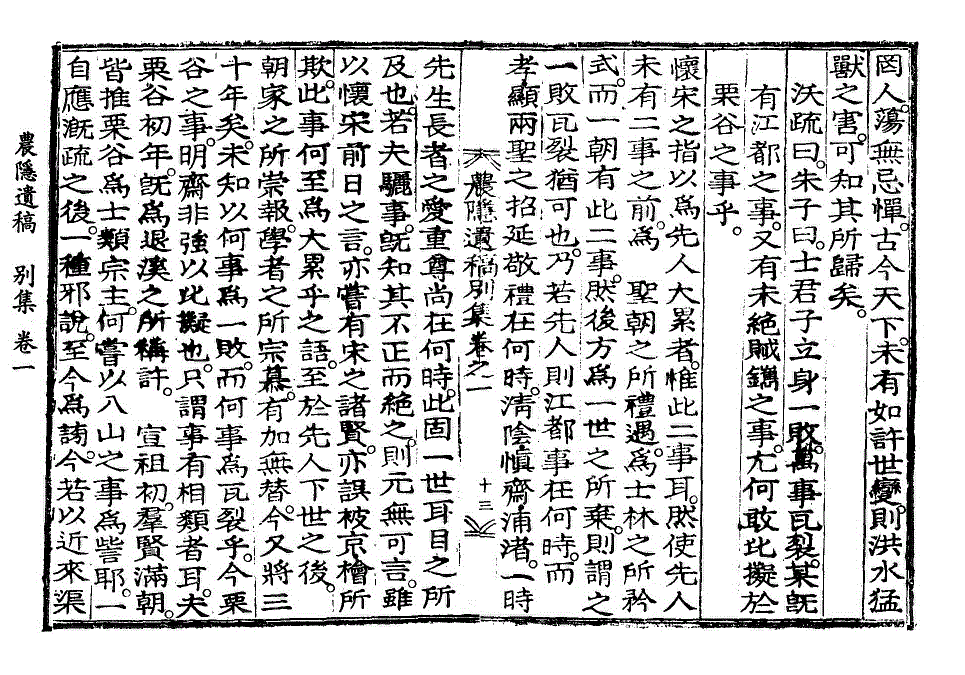 罔人。荡无忌惮。古今天下。未有如许世变。则洪水猛兽之害。可知其所归矣。
罔人。荡无忌惮。古今天下。未有如许世变。则洪水猛兽之害。可知其所归矣。沃疏曰。朱子曰。士君子立身一败。万事瓦裂。某既有江都之事。又有未绝贼镌之事。尤何敢比拟于栗谷之事乎。
怀宋之指以为先人大累者。惟此二事耳。然使先人未有二事之前。为 圣朝之所礼遇。为士林之所矜式。而一朝有此二事。然后方为一世之所弃。则谓之一败瓦裂犹可也。乃若先人则江都事在何时。而 孝,显两圣之招延敬礼在何时。清阴,慎斋,浦渚。一时先生长者之爱重尊尚在何时。此固一世耳目之所及也。若夫骊事。既知其不正而绝之。则元无可言。虽以怀宋前日之言。亦尝有宋之诸贤。亦误被京,桧所欺。此事何至为大累乎之语。至于先人下世之后。 朝家之所崇报。学者之所宗慕。有加无替。今又将三十年矣。未知以何事为一败。而何事为瓦裂乎。今栗谷之事。明斋非强以比拟也。只谓事有相类者耳。夫栗谷初年。既为退溪之所称许。 宣祖初。群贤满朝。皆推栗谷为士类宗主。何尝以入山之事为訾耶。一自应溉疏之后。一种邪说。至今为谤。今若以近来渠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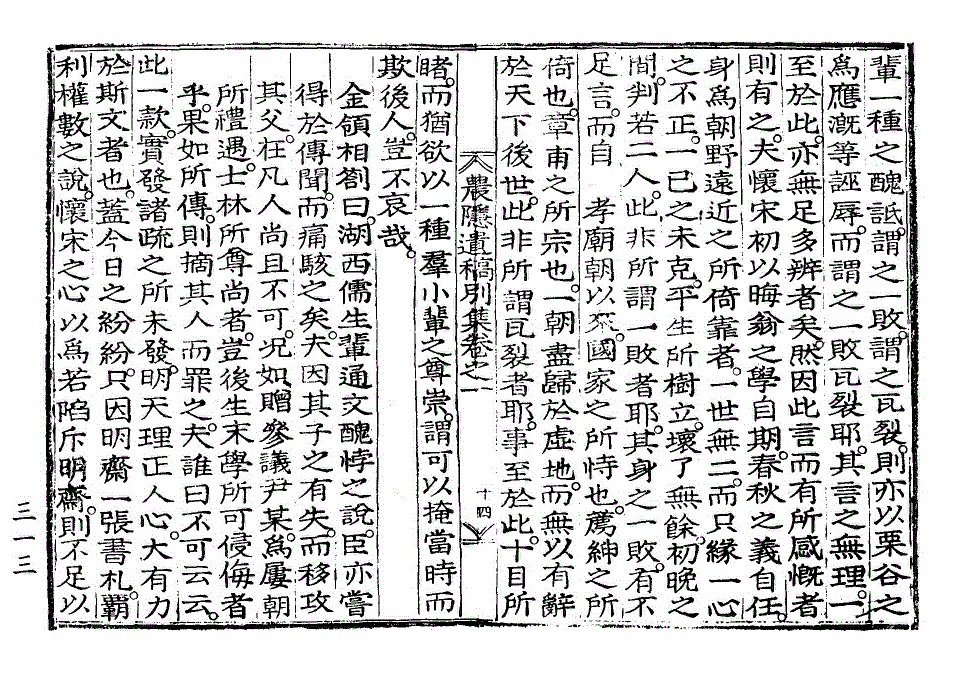 辈一种之丑诋。谓之一败。谓之瓦裂。则亦以栗谷之为应溉等诬辱。而谓之一败瓦裂耶。其言之无理。一至于此。亦无足多辨者矣。然因此言而有所感慨者则有之。夫怀宋初以晦翁之学自期。春秋之义自任。身为朝野远近之所倚靠者。一世无二。而只缘一心之不正。一己之未克。平生所树立。坏了无馀。初晚之间。判若二人。此非所谓一败者耶。其身之一败。有不足言。而自 孝庙朝以来。国家之所恃也。荐绅之所倚也。章甫之所宗也。一朝尽归于虚地。而无以有辞于天下后世。此非所谓瓦裂者耶。事至于此。十目所睹。而犹欲以一种群小辈之尊崇。谓可以掩当时而欺后人。岂不哀哉。
辈一种之丑诋。谓之一败。谓之瓦裂。则亦以栗谷之为应溉等诬辱。而谓之一败瓦裂耶。其言之无理。一至于此。亦无足多辨者矣。然因此言而有所感慨者则有之。夫怀宋初以晦翁之学自期。春秋之义自任。身为朝野远近之所倚靠者。一世无二。而只缘一心之不正。一己之未克。平生所树立。坏了无馀。初晚之间。判若二人。此非所谓一败者耶。其身之一败。有不足言。而自 孝庙朝以来。国家之所恃也。荐绅之所倚也。章甫之所宗也。一朝尽归于虚地。而无以有辞于天下后世。此非所谓瓦裂者耶。事至于此。十目所睹。而犹欲以一种群小辈之尊崇。谓可以掩当时而欺后人。岂不哀哉。金领相劄曰。湖西儒生辈通文丑悖之说。臣亦尝得于传闻。而痛骇之矣。夫因其子之有失。而移攻其父。在凡人尚且不可。况如赠参议尹某。为屡朝所礼遇。士林所尊尚者。岂后生末学所可侵侮者乎。果如所传。则摘其人而罪之。夫谁曰不可云云。
此一款。实发诸疏之所未发。明天理正人心。大有力于斯文者也。盖今日之纷纷。只因明斋一张书札。霸利权数之说。怀宋之心以为若陷斥明斋。则不足以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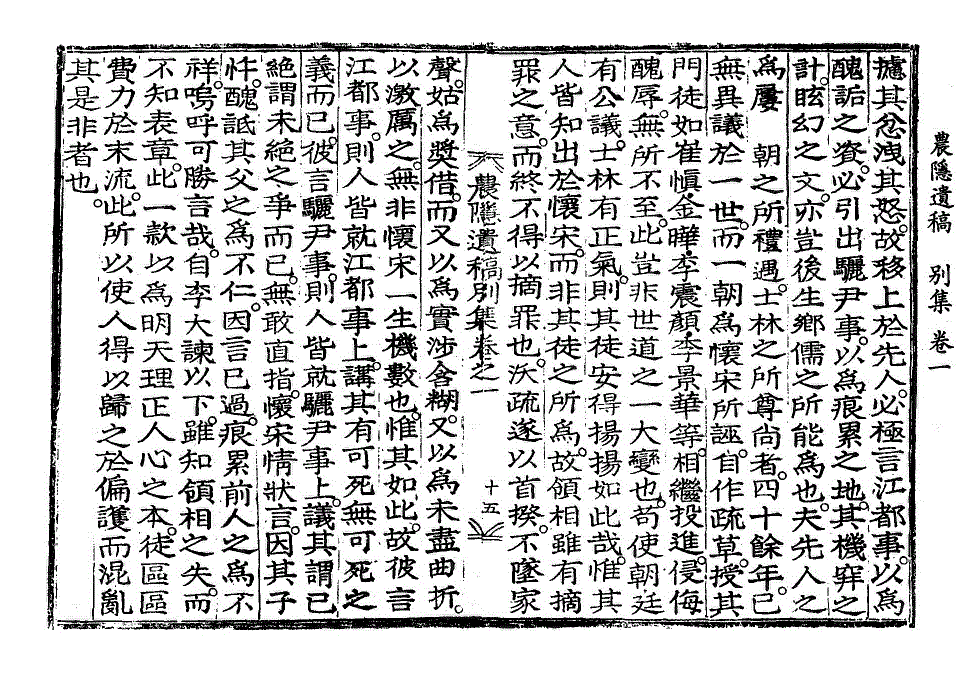 摅其忿泄其怒。故移上于先人。必极言江都事。以为丑诟之资。必引出骊尹事。以为痕累之地。其机阱之计。眩幻之文。亦岂后生乡儒之所能为也。夫先人之为屡 朝之所礼遇。士林之所尊尚者。四十馀年。已无异议于一世。而一朝为怀宋所诬。自作疏草。授其门徒如崔慎,金晔,李震颜,李景华等。相继投进。侵侮丑辱。无所不至。此岂非世道之一大变也。苟使朝廷有公议。士林有正气。则其徒安得扬扬如此哉。惟其人皆知出于怀宋。而非其徒之所为。故领相虽有摘罪之意。而终不得以摘罪也。沃疏遂以首揆。不坠家声。姑为奖借。而又以为实涉含糊。又以为未尽曲折。以激厉之。无非怀宋一生机数也。惟其如此。故彼言江都事。则人皆就江都事上。讲其有可死无可死之义而已。彼言骊尹事。则人皆就骊尹事上。议其谓已绝谓未绝之争而已。无敢直指。怀宋情状言。因其子忤。丑诋其父之为不仁。因言已过。痕累前人之为不祥。呜呼可胜言哉。自李大谏以下。虽知领相之失。而不知表章。此一款以为明天理正人心之本。徒区区费力于末流。此所以使人得以归之于偏护而混乱其是非者也。
摅其忿泄其怒。故移上于先人。必极言江都事。以为丑诟之资。必引出骊尹事。以为痕累之地。其机阱之计。眩幻之文。亦岂后生乡儒之所能为也。夫先人之为屡 朝之所礼遇。士林之所尊尚者。四十馀年。已无异议于一世。而一朝为怀宋所诬。自作疏草。授其门徒如崔慎,金晔,李震颜,李景华等。相继投进。侵侮丑辱。无所不至。此岂非世道之一大变也。苟使朝廷有公议。士林有正气。则其徒安得扬扬如此哉。惟其人皆知出于怀宋。而非其徒之所为。故领相虽有摘罪之意。而终不得以摘罪也。沃疏遂以首揆。不坠家声。姑为奖借。而又以为实涉含糊。又以为未尽曲折。以激厉之。无非怀宋一生机数也。惟其如此。故彼言江都事。则人皆就江都事上。讲其有可死无可死之义而已。彼言骊尹事。则人皆就骊尹事上。议其谓已绝谓未绝之争而已。无敢直指。怀宋情状言。因其子忤。丑诋其父之为不仁。因言已过。痕累前人之为不祥。呜呼可胜言哉。自李大谏以下。虽知领相之失。而不知表章。此一款以为明天理正人心之本。徒区区费力于末流。此所以使人得以归之于偏护而混乱其是非者也。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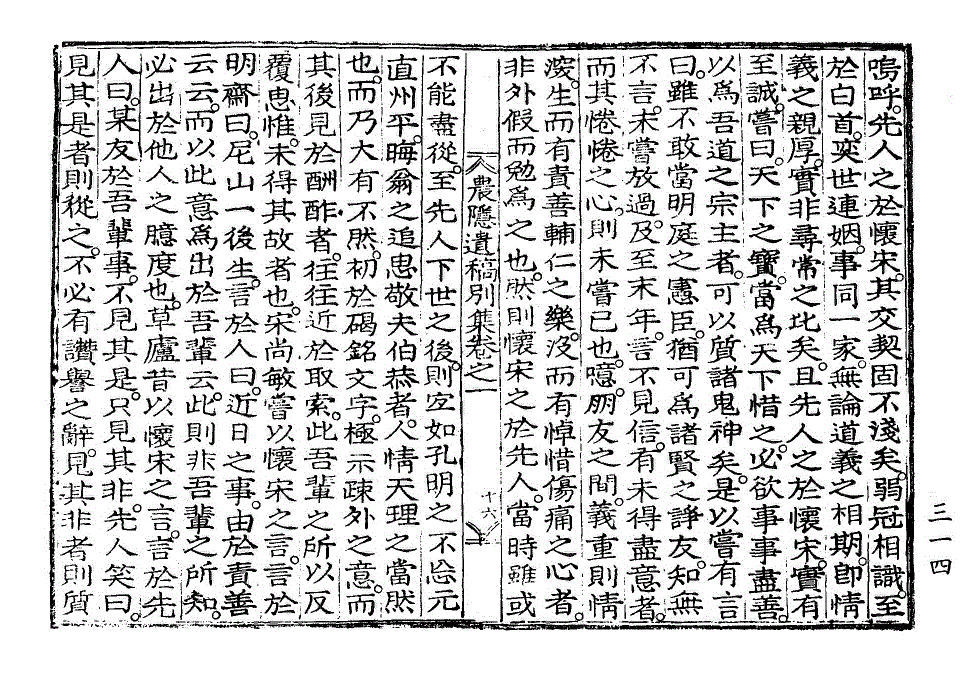 呜呼。先人之于怀宋。其交契固不浅矣。弱冠相识。至于白首。奕世连姻。事同一家。无论道义之相期。即情义之亲厚。实非寻常之比矣。且先人之于怀宋。实有至诚。尝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必欲事事尽善。以为吾道之宗主者。可以质诸鬼神矣。是以尝有言曰。虽不敢当明庭之宪臣。犹可为诸贤之诤友。知无不言。未尝放过。及至末年。言不见信。有未得尽意者。而其惓惓之心。则未尝已也。噫。朋友之间。义重则情深。生而有责善辅仁之乐。没而有悼惜伤痛之心者。非外假而勉为之也。然则怀宋之于先人。当时虽或不能尽从。至先人下世之后。则宜如孔明之不忘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者。人情天理之当然也。而乃大有不然。初于碣铭文字。极示疏外之意。而其后见于酬酢者。往往近于取索。此吾辈之所以反覆思惟。未得其故者也。宋尚敏尝以怀宋之言。言于明斋曰。尼山一后生。言于人曰。近日之事。由于责善云云。而以此意为出于吾辈云。此则非吾辈之所知。必出于他人之臆度也。草庐昔以怀宋之言。言于先人曰。某友于吾辈事。不见其是。只见其非。先人笑曰。见其是者则从之。不必有赞誉之辞。见其非者则质
呜呼。先人之于怀宋。其交契固不浅矣。弱冠相识。至于白首。奕世连姻。事同一家。无论道义之相期。即情义之亲厚。实非寻常之比矣。且先人之于怀宋。实有至诚。尝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必欲事事尽善。以为吾道之宗主者。可以质诸鬼神矣。是以尝有言曰。虽不敢当明庭之宪臣。犹可为诸贤之诤友。知无不言。未尝放过。及至末年。言不见信。有未得尽意者。而其惓惓之心。则未尝已也。噫。朋友之间。义重则情深。生而有责善辅仁之乐。没而有悼惜伤痛之心者。非外假而勉为之也。然则怀宋之于先人。当时虽或不能尽从。至先人下世之后。则宜如孔明之不忘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者。人情天理之当然也。而乃大有不然。初于碣铭文字。极示疏外之意。而其后见于酬酢者。往往近于取索。此吾辈之所以反覆思惟。未得其故者也。宋尚敏尝以怀宋之言。言于明斋曰。尼山一后生。言于人曰。近日之事。由于责善云云。而以此意为出于吾辈云。此则非吾辈之所知。必出于他人之臆度也。草庐昔以怀宋之言。言于先人曰。某友于吾辈事。不见其是。只见其非。先人笑曰。见其是者则从之。不必有赞誉之辞。见其非者则质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5H 页
 之。不能无攻砭之言。然则必面相赞誉而后谓之见其是乎。草庐又曰。君与尤庵。每相辨争。尤庵书之。以传于后则柰何。先人又笑曰。惟惧吾见之未必是当耳。尤庵之书。吾不畏也。书而不公。谁复信之。先人己酉。遗札之与怀宋者。有曰。欲吾君之无私意。当先去吾之私意。欲吾君之开言路。当先开吾之言路。宋掌令基厚。见此语不觉击节叹赏。以为切中尤庵之病也。今以此数语。溯而论之。怀宋之于先人。其终始不相契者。庶可想矣。既不能纳。则又从而疑之。自古交际之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者何限。然则或人所谓由于责善云者。似不虚矣。仍切惟念先人之学。慥慥以守约为务。怀宋之学。堂堂以卫道自任。其始也。固如文质之相须。似不可偏废者。而怀宋之主张太过。自引太高。乘之以气质之刚。助之以权位之重。于是尚同之风成。而逆耳之言绝。自克之诚心不立。而力服之形势渐张。其欲质疑发难救阙补弊之言。一切归之于异己异论。驯致于自圣孤立之地。然则其谓人之不己知而追仇尽言者。怀宋亦有不能自觉者矣。此先人之诚意所以见阻于终始者。而古人所谓忧人太过。以德取怨者不幸而近之矣。惟其有此根
之。不能无攻砭之言。然则必面相赞誉而后谓之见其是乎。草庐又曰。君与尤庵。每相辨争。尤庵书之。以传于后则柰何。先人又笑曰。惟惧吾见之未必是当耳。尤庵之书。吾不畏也。书而不公。谁复信之。先人己酉。遗札之与怀宋者。有曰。欲吾君之无私意。当先去吾之私意。欲吾君之开言路。当先开吾之言路。宋掌令基厚。见此语不觉击节叹赏。以为切中尤庵之病也。今以此数语。溯而论之。怀宋之于先人。其终始不相契者。庶可想矣。既不能纳。则又从而疑之。自古交际之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者何限。然则或人所谓由于责善云者。似不虚矣。仍切惟念先人之学。慥慥以守约为务。怀宋之学。堂堂以卫道自任。其始也。固如文质之相须。似不可偏废者。而怀宋之主张太过。自引太高。乘之以气质之刚。助之以权位之重。于是尚同之风成。而逆耳之言绝。自克之诚心不立。而力服之形势渐张。其欲质疑发难救阙补弊之言。一切归之于异己异论。驯致于自圣孤立之地。然则其谓人之不己知而追仇尽言者。怀宋亦有不能自觉者矣。此先人之诚意所以见阻于终始者。而古人所谓忧人太过。以德取怨者不幸而近之矣。惟其有此根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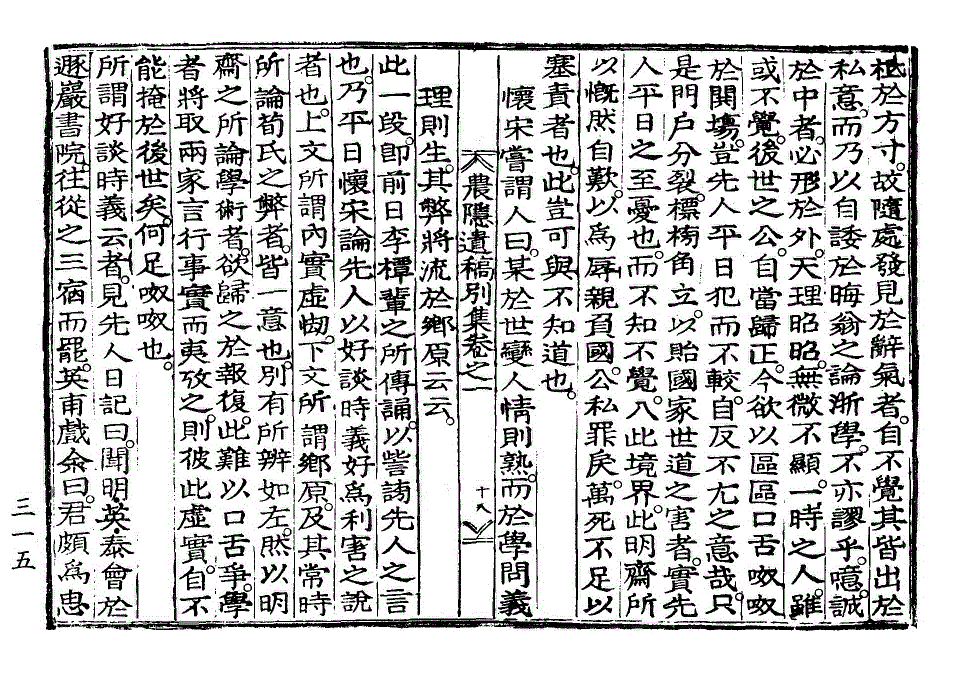 柢于方寸。故随处发见于辞气者。自不觉其皆出于私意。而乃以自诿于晦翁之论浙学。不亦谬乎。噫。诚于中者。必形于外。天理昭昭。无微不显。一时之人。虽或不觉。后世之公。自当归正。今欲以区区口舌呶呶于鬨场。岂先人平日犯而不较。自反不尤之意哉。只是门户分裂。标榜角立。以贻国家世道之害者。实先人平日之至忧也。而不知不觉。入此境界。此明斋所以慨然自叹。以为辱亲负国。公私罪戾。万死不足以塞责者也。此岂可与不知道也。
柢于方寸。故随处发见于辞气者。自不觉其皆出于私意。而乃以自诿于晦翁之论浙学。不亦谬乎。噫。诚于中者。必形于外。天理昭昭。无微不显。一时之人。虽或不觉。后世之公。自当归正。今欲以区区口舌呶呶于鬨场。岂先人平日犯而不较。自反不尤之意哉。只是门户分裂。标榜角立。以贻国家世道之害者。实先人平日之至忧也。而不知不觉。入此境界。此明斋所以慨然自叹。以为辱亲负国。公私罪戾。万死不足以塞责者也。此岂可与不知道也。怀宋尝谓人曰。某于世变人情则熟。而于学问义理则生。其弊将流于乡原云云。
此一段。即前日李橝辈之所传诵。以訾谤先人之言也。乃平日怀宋论先人以好谈时义好为利害之说者也。上文所谓内实虚劫。下文所谓乡原。及其常时所论荀氏之弊者。皆一意也。别有所辨如左。然以明斋之所论学术者。欲归之于报复。此难以口舌争。学者将取两家言行事实而夷考之。则彼此虚实。自不能掩于后世矣。何足呶呶也。
所谓好谈时义云者。见先人日记曰。闻明,英,泰会于遁岩书院。往从之三宿而罢。英甫戏余曰。君颇为思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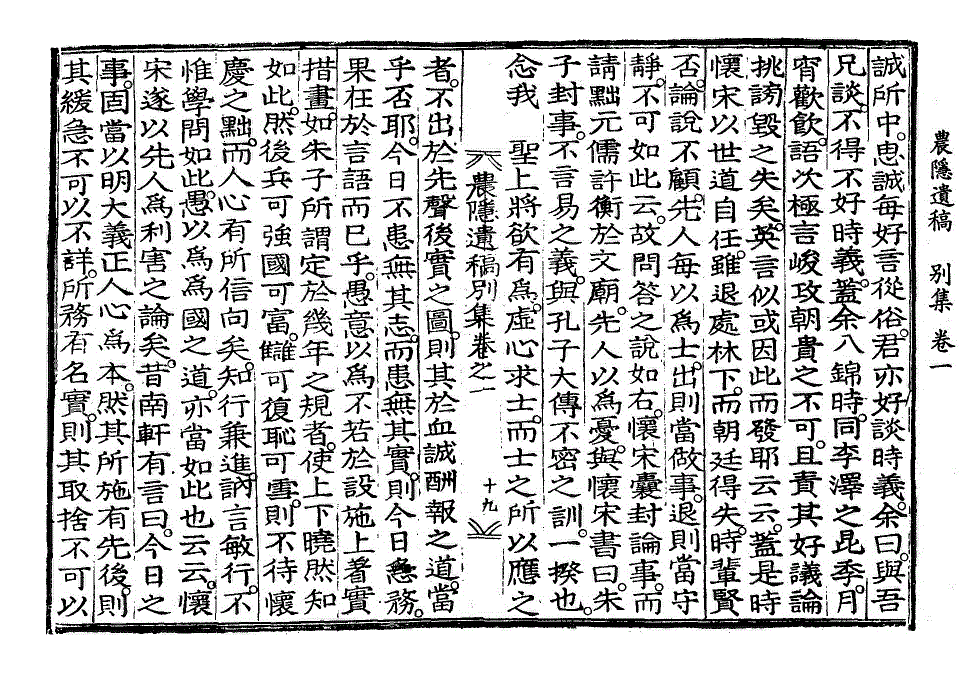 诚所中。思诚每好言从俗。君亦好谈时义。余曰。与吾兄谈。不得不好时义。盖余入锦时。同李泽之昆季。月宵欢饮。语次极言峻攻朝贵之不可。且责其好议论挑谤毁之失矣。英言似或因此而发耶云云。盖是时怀宋以世道自任。虽退处林下。而朝廷得失。时辈贤否。论说不顾。先人每以为士。出则当做事。退则当守静。不可如此云。故问答之说如右。怀宋囊封论事。而请黜元儒许衡于文庙。先人以为忧。与怀宋书曰。朱子封事。不言易之义。与孔子大传不密之训。一揆也。念我 圣上将欲有为。虚心求士。而士之所以应之者。不出于先声后实之图。则其于血诚酬报之道。当乎否耶。今日不患无其志。而患无其实。则今日急务。果在于言语而已乎。愚意以为不若于设施上着实措画。如朱子所谓定于几年之规者。使上下晓然知如此。然后兵可强国可富。雠可复耻可雪。则不待怀庆之黜。而人心有所信向矣。知行兼进。讷言敏行。不惟学问如此。愚以为为国之道。亦当如此也云云。怀宋遂以先人为利害之论矣。昔南轩有言曰。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然其所施有先后。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所务有名实。则其取舍不可以
诚所中。思诚每好言从俗。君亦好谈时义。余曰。与吾兄谈。不得不好时义。盖余入锦时。同李泽之昆季。月宵欢饮。语次极言峻攻朝贵之不可。且责其好议论挑谤毁之失矣。英言似或因此而发耶云云。盖是时怀宋以世道自任。虽退处林下。而朝廷得失。时辈贤否。论说不顾。先人每以为士。出则当做事。退则当守静。不可如此云。故问答之说如右。怀宋囊封论事。而请黜元儒许衡于文庙。先人以为忧。与怀宋书曰。朱子封事。不言易之义。与孔子大传不密之训。一揆也。念我 圣上将欲有为。虚心求士。而士之所以应之者。不出于先声后实之图。则其于血诚酬报之道。当乎否耶。今日不患无其志。而患无其实。则今日急务。果在于言语而已乎。愚意以为不若于设施上着实措画。如朱子所谓定于几年之规者。使上下晓然知如此。然后兵可强国可富。雠可复耻可雪。则不待怀庆之黜。而人心有所信向矣。知行兼进。讷言敏行。不惟学问如此。愚以为为国之道。亦当如此也云云。怀宋遂以先人为利害之论矣。昔南轩有言曰。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然其所施有先后。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所务有名实。则其取舍不可以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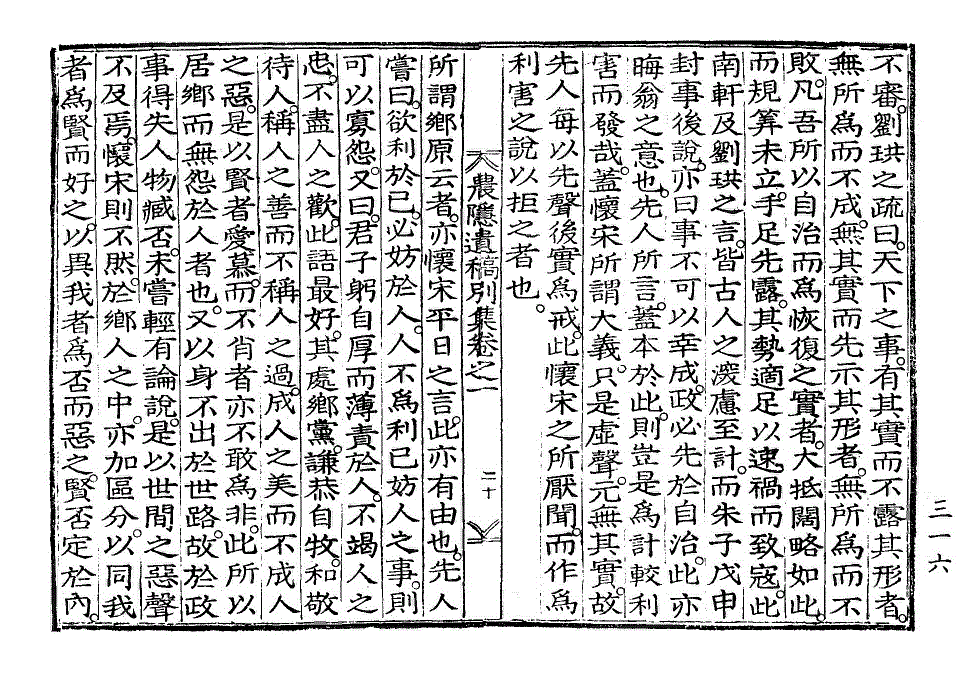 不审。刘珙之疏曰。天下之事。有其实而不露其形者。无所为而不成。无其实而先示其形者。无所为而不败。凡吾所以自治而为恢复之实者。大抵阔略如此。而规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势适足以速祸而致寇。此南轩及刘珙之言。皆古人之深虑至计。而朱子戊申封事后说。亦曰事不可以幸成。政必先于自治。此亦晦翁之意也。先人所言。盖本于此。则岂是为计较利害而发哉。盖怀宋所谓大义。只是虚声。元无其实。故先人每以先声后实为戒。此怀宋之所厌闻。而作为利害之说以拒之者也。
不审。刘珙之疏曰。天下之事。有其实而不露其形者。无所为而不成。无其实而先示其形者。无所为而不败。凡吾所以自治而为恢复之实者。大抵阔略如此。而规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势适足以速祸而致寇。此南轩及刘珙之言。皆古人之深虑至计。而朱子戊申封事后说。亦曰事不可以幸成。政必先于自治。此亦晦翁之意也。先人所言。盖本于此。则岂是为计较利害而发哉。盖怀宋所谓大义。只是虚声。元无其实。故先人每以先声后实为戒。此怀宋之所厌闻。而作为利害之说以拒之者也。所谓乡原云者。亦怀宋平日之言。此亦有由也。先人尝曰。欲利于己。必妨于人。人不为利己妨人之事。则可以寡怨。又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竭人之忠。不尽人之欢。此语最好。其处乡党。谦恭自牧。和敬待人。称人之善而不称人之过。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是以贤者爱慕。而不肖者亦不敢为非。此所以居乡而无怨于人者也。又以身不出于世路。故于政事得失人物臧否。未尝轻有论说。是以世间之恶声不及焉。怀宋则不然。于乡人之中。亦加区分。以同我者为贤而好之。以异我者为否而恶之。贤否定于内。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7H 页
 而好恶施于外。于是缉言而贡忠者有之。讦人而搆怨者有之。彼此立而攻击生焉。至于立朝。亦以此道施之。以此到处无非鬨场。盖道之不同者如此。故自托于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之圣训。而反欲以众皆悦之之目。加之于先人。殊不知其好之者未必善者。恶之者未必不善者。而所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者。独非圣训乎。狡伪献诚。暴慢致恭。贤愚善恶。咸得其心者。非明道之遗矩乎。且乡原者。其心主于随世谐俗。同流合污而已。如先人之特立独行守道固穷。虽朋友之间。亦不能俯仰苟合。则与所谓原人者。岂非百千万里之远。强以是勒诋之耶。
而好恶施于外。于是缉言而贡忠者有之。讦人而搆怨者有之。彼此立而攻击生焉。至于立朝。亦以此道施之。以此到处无非鬨场。盖道之不同者如此。故自托于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之圣训。而反欲以众皆悦之之目。加之于先人。殊不知其好之者未必善者。恶之者未必不善者。而所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者。独非圣训乎。狡伪献诚。暴慢致恭。贤愚善恶。咸得其心者。非明道之遗矩乎。且乡原者。其心主于随世谐俗。同流合污而已。如先人之特立独行守道固穷。虽朋友之间。亦不能俯仰苟合。则与所谓原人者。岂非百千万里之远。强以是勒诋之耶。所谓荀氏之弊云者。怀宋尝引朱子所论。(与刘子澄书)以为先人之訾谤。至以聚星亭赞书付壁上。而说与于后生辈。故相与传习。又几于成一话头。此亦有由也。盖向来怀宋之主张时论也。先人每举其不厌于人心者以规之。则固反疑先人之流徇物情矣。及以礼论同异。排抑一边收司之律。至于已甚。间有外托扶抑之义。实济党伐之私者。怀宋终始为之宗主。而先人常持平心去私损过就中之论。怀宋既不能纳。则又反以致疑如上文所谓熟于世故者。故其时炭翁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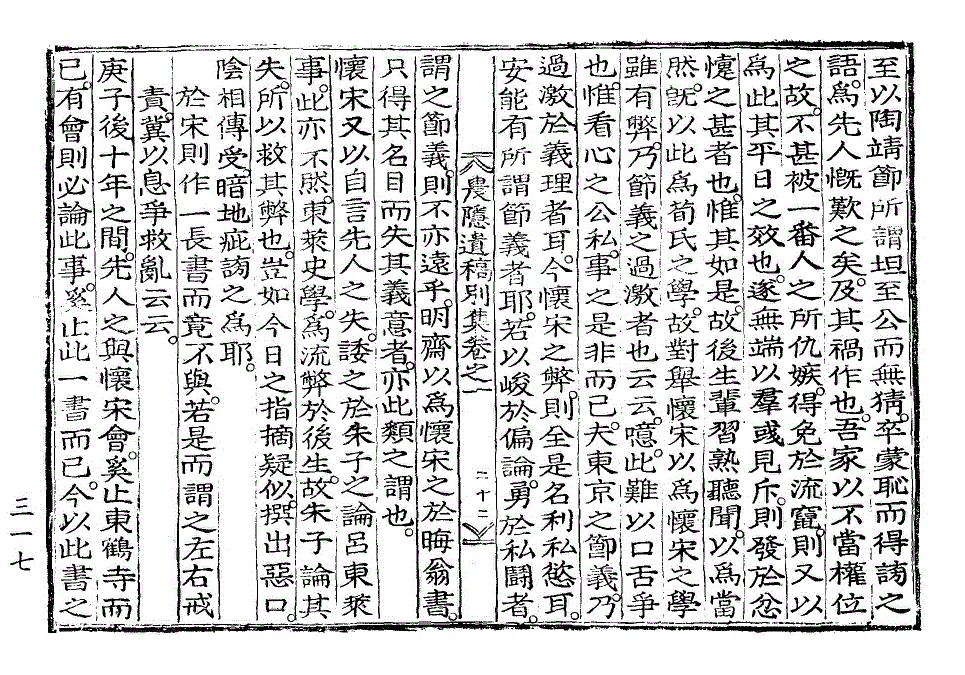 至以陶靖节所谓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而得谤之语。为先人慨叹之矣。及其祸作也。吾家以不当权位之故。不甚被一番人之所仇嫉。得免于流窜。则又以为此其平日之效也。遂无端以群彧见斥。则发于忿懥之甚者也。惟其如是。故后生辈习熟听闻。以为当然。既以此为荀氏之学。故对举怀宋以为怀宋之学虽有弊。乃节义之过激者也云云。噫。此难以口舌争也。惟看心之公私。事之是非而已。夫东京之节义。乃过激于义理者耳。今怀宋之弊。则全是名利私欲耳。安能有所谓节义者耶。若以峻于偏论。勇于私斗者。谓之节义。则不亦远乎。明斋以为怀宋之于晦翁书。只得其名目而失其义意者。亦此类之谓也。
至以陶靖节所谓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而得谤之语。为先人慨叹之矣。及其祸作也。吾家以不当权位之故。不甚被一番人之所仇嫉。得免于流窜。则又以为此其平日之效也。遂无端以群彧见斥。则发于忿懥之甚者也。惟其如是。故后生辈习熟听闻。以为当然。既以此为荀氏之学。故对举怀宋以为怀宋之学虽有弊。乃节义之过激者也云云。噫。此难以口舌争也。惟看心之公私。事之是非而已。夫东京之节义。乃过激于义理者耳。今怀宋之弊。则全是名利私欲耳。安能有所谓节义者耶。若以峻于偏论。勇于私斗者。谓之节义。则不亦远乎。明斋以为怀宋之于晦翁书。只得其名目而失其义意者。亦此类之谓也。怀宋又以自言先人之失。诿之于朱子之论吕东莱事。此亦不然。东莱史学。为流弊于后生。故朱子论其失。所以救其弊也。岂如今日之指摘疑似。撰出恶口。阴相传受。暗地疵谤之为耶。
于宋则作一长书而竟不与。若是而谓之左右戒责。冀以息争救乱云云。
庚子后十年之间。先人之与怀宋会。奚止东鹤寺而已。有会则必论此事。奚止此一书而已。今以此书之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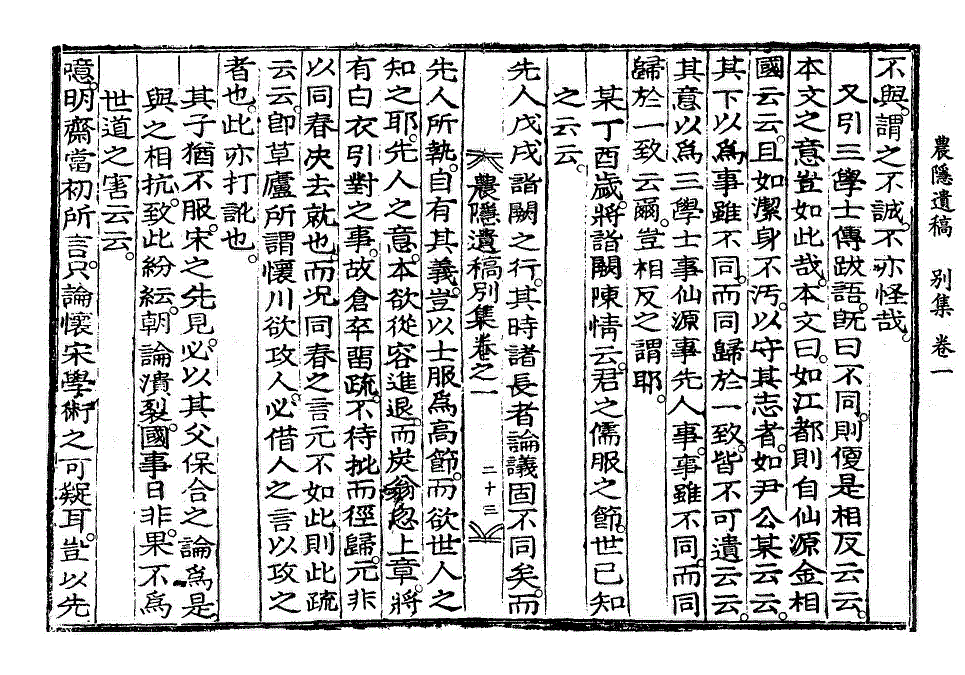 不与。谓之不诚。不亦怪哉。
不与。谓之不诚。不亦怪哉。又引三学士传跋语。既曰不同。则便是相反云云。
本文之意岂如此哉。本文曰。如江都则自仙源金相国云云。且如洁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某云云。其下以为事虽不同。而同归于一致。皆不可遗云云。其意以为三学士事仙源事先人事。事虽不同。而同归于一致云尔。岂相反之谓耶。
某丁酉岁。将诣阙陈情云。君之儒服之节。世已知之云云。
先人戊戌诣阙之行。其时诸长者论议固不同矣。而先人所执。自有其义。岂以士服为高节。而欲世人之知之耶。先人之意。本欲从容进退。而炭翁忽上章。将有白衣引对之事。故仓卒留疏。不待批而径归。元非以同春决去就也。而况同春之言元不如此则此疏云云。即草庐所谓怀川欲攻人。必借人之言以攻之者也。此亦打讹也。
其子犹不服。宋之先见。必以其父保合之论为是。与之相抗。致此纷纭。朝论溃裂。国事日非。果不为世道之害云云。
噫。明斋当初所言。只论怀宋学术之可疑耳。岂以先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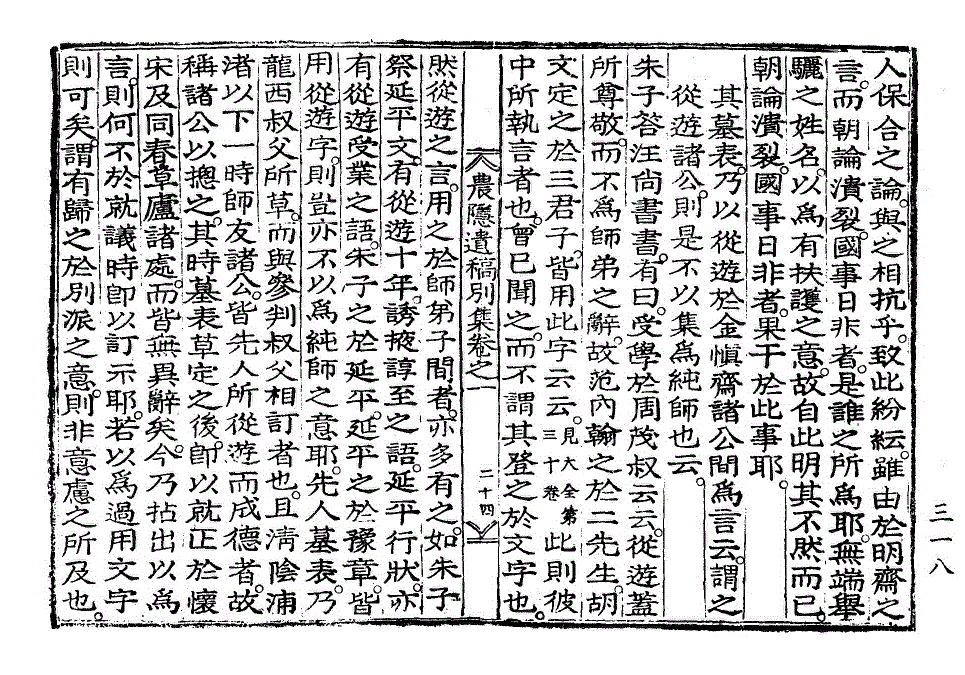 人保合之论。与之相抗乎。致此纷纭。虽由于明斋之言。而朝论溃裂。国事日非者。是谁之所为耶。无端举骊之姓名。以为有扶护之意。故自此明其不然而已。朝论溃裂。国事日非者。果干于此事耶。
人保合之论。与之相抗乎。致此纷纭。虽由于明斋之言。而朝论溃裂。国事日非者。是谁之所为耶。无端举骊之姓名。以为有扶护之意。故自此明其不然而已。朝论溃裂。国事日非者。果干于此事耶。其墓表。乃以从游于金慎斋诸公间为言云。谓之从游诸公。则是不以集为纯师也云。
朱子答汪尚书书。有曰。受学于周茂叔云云。从游盖所尊敬。而不为师弟之辞。故范内翰之于二先生。胡文定之于三君子。皆用此字云云。(见大全第三十卷)此则彼中所执言者也。曾已闻之。而不谓其登之于文字也。然从游之言。用之于师弟子间者。亦多有之。如朱子祭延平文。有从游十年。诱掖谆至之语。延平行状。亦有从游受业之语。朱子之于延平。延平之于豫章。皆用从游字。则岂亦不以为纯师之意耶。先人墓表。乃龙西叔父所草。而与参判叔父相订者也。且清阴浦渚以下一时师友诸公。皆先人所从游而成德者。故称诸公以总之。其时墓表草定之后。即以就正于怀宋及同春,草庐诸处。而皆无异辞矣。今乃拈出以为言。则何不于就议时即以订示耶。若以为过用文字则可矣。谓有归之于别派之意。则非意虑之所及也。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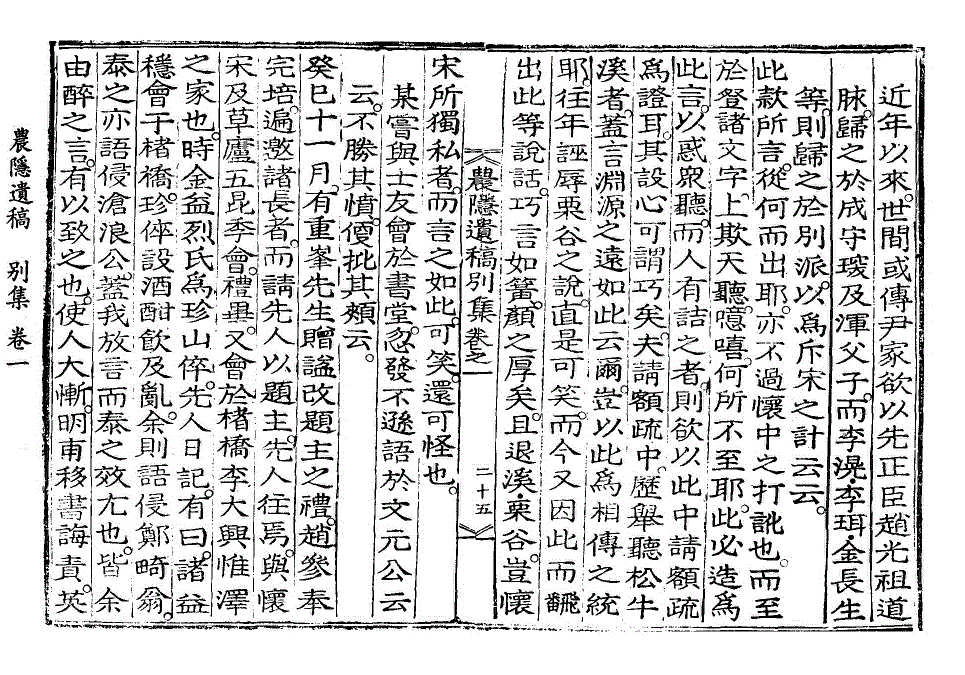 近年以来。世间或传尹家欲以先正臣赵光祖道脉。归之于成守琛及浑父子。而李滉,李珥,金长生等。则归之于别派。以为斥宋之计云云。
近年以来。世间或传尹家欲以先正臣赵光祖道脉。归之于成守琛及浑父子。而李滉,李珥,金长生等。则归之于别派。以为斥宋之计云云。此款所言。从何而出耶。亦不过怀中之打讹也。而至于登诸文字。上欺天听。噫嘻。何所不至耶。此必造为此言。以惑众听。而人有诘之者。则欲以此中请额疏为證耳。其设心可谓巧矣。夫请额疏中。历举听松牛溪者。盖言渊源之远如此云尔。岂以此为相传之统耶。往年诬辱栗谷之说。直是可笑。而今又因此而翻出此等说话。巧言如簧。颜之厚矣。且退溪,栗谷。岂怀宋所独私者。而言之如此。可笑。还可怪也。
某尝与士友会于书堂。忽发不逊语于文元公云云。不胜其愤。便批其颊云。
癸巳十一月。有重峰先生赠谥改题主之礼。赵参奉完培。遍邀诸长者。而请先人以题主。先人往焉。与怀宋及草庐五昆季会。礼毕。又会于楮桥李大兴惟泽之家也。时金益烈氏为珍山倅。先人日记。有曰。诸益稳会于楮桥。珍倅设酒酣饮及乱。余则语侵郑畸翁。泰之亦语侵沧浪公。盖我放言而泰之效尤也。皆余由醉之言。有以致之也。使人大惭。明甫移书诲责。英
农隐先生遗稿别集卷之一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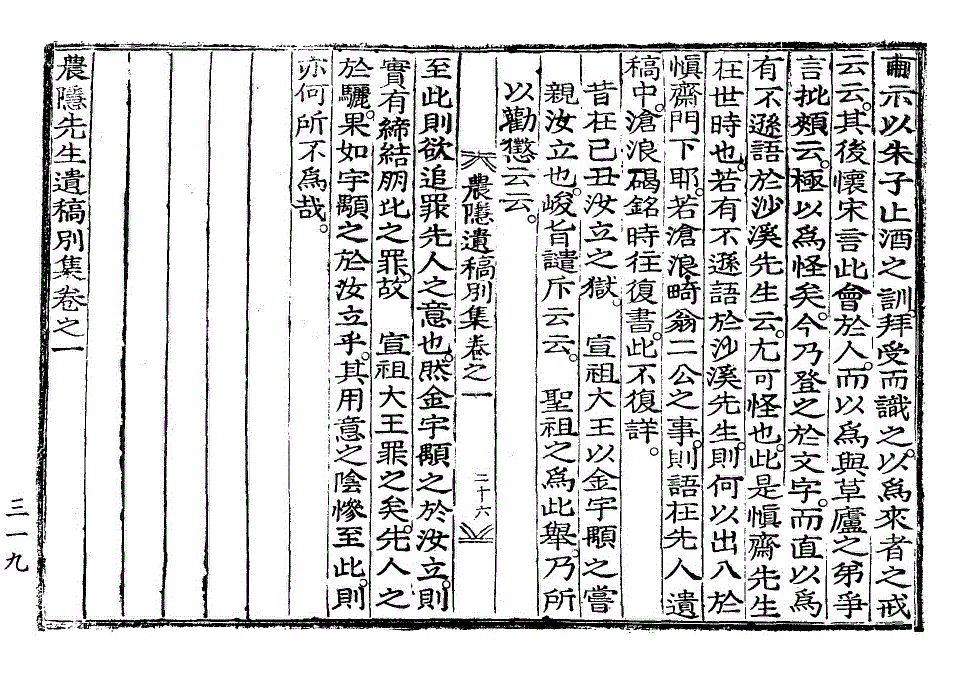 甫示以朱子止酒之训。拜受而识之。以为来者之戒云云。其后怀宋言此会于人。而以为与草庐之弟争言批颊云。极以为怪矣。今乃登之于文字。而直以为有不逊语于沙溪先生云。尤可怪也。此是慎斋先生在世时也。若有不逊语于沙溪先生。则何以出入于慎斋门下耶。若沧浪,畸翁二公之事。则语在先人遗稿中。沧浪碣铭时往复书。此不复详。
甫示以朱子止酒之训。拜受而识之。以为来者之戒云云。其后怀宋言此会于人。而以为与草庐之弟争言批颊云。极以为怪矣。今乃登之于文字。而直以为有不逊语于沙溪先生云。尤可怪也。此是慎斋先生在世时也。若有不逊语于沙溪先生。则何以出入于慎斋门下耶。若沧浪,畸翁二公之事。则语在先人遗稿中。沧浪碣铭时往复书。此不复详。昔在己丑汝立之狱。 宣祖大王以金宇颙之尝亲汝立也。峻旨谴斥云云。 圣祖之为此举。乃所以劝惩云云。
至此则欲追罪先人之意也。然金宇颙之于汝立。则实有缔结朋比之罪。故 宣祖大王罪之矣。先人之于骊。果如宇颙之于汝立乎。其用意之阴惨至此。则亦何所不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