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x 页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年谱]
[年谱]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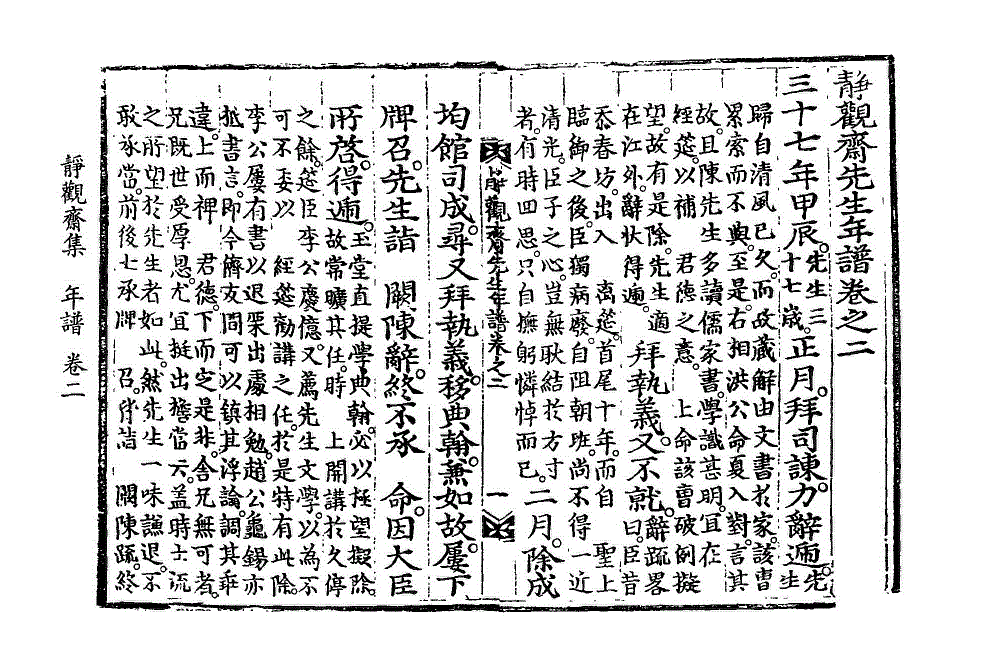 静观斋先生年谱[二]
静观斋先生年谱[二]三十七年甲辰。(先生三十七岁。)正月。拜司谏。力辞递。(先生归自清风已久。而故藏解由文书于家。该曹累索而不与。至是。右相洪公命夏入对。言其故。且陈先生多读儒家书。学识甚明。宜在 经筵。以补 君德之意。 上命该曹破例拟望。故有是除。先生适在江外。辞状得递。)拜执义。又不就。(辞疏略曰。臣昔忝春坊。出入 离筵。首尾十年。而自 圣上临御之后。臣独病废。自阻朝班。尚不得一近清光。臣子之心。岂无耿结于方寸者。有时回思。只自抚躬怜悼而已。)二月。除成均馆司成。寻又拜执义。移典翰。兼如故。屡下牌召。先生诣 阙陈辞。终不承 命。因大臣所启。得递。(玉堂直提学,典翰。必以极望拟除。故常旷其任。时 上开讲于久停之馀。筵臣李公庆亿。又荐先生文学。以为不可不委以 经筵劝讲之任。于是特有此除。李公屡有书以退,栗出处相勉。赵公龟锡亦抵书言。即今侪友间可以镇其浮论。调其乖违。上而裨 君德。下而定是非。舍兄无可者。兄既世受厚恩。尤宜挺出担当云。盖时士流之所望于先生者如此。然先生一味谦退。不敢承当。前后七承牌 召。皆诣 阙陈疏。终)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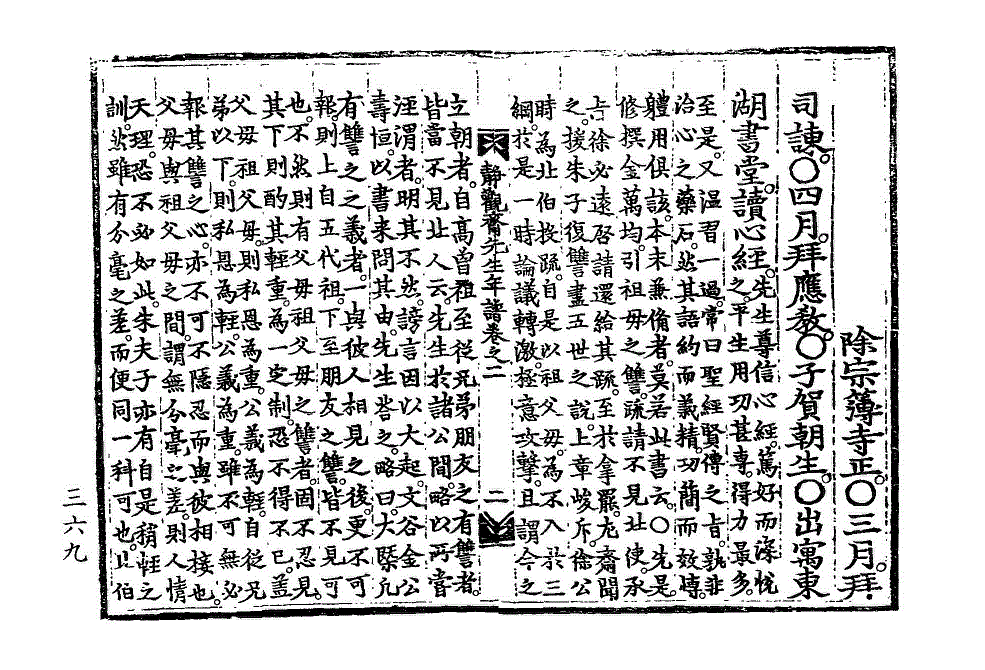 ▣▣▣▣▣▣▣▣除宗簿寺正。○三月。拜司谏。○四月。拜应教。○子贺朝生。○出寓东湖书堂。读心经。(先生尊信心经。笃好而深悦之。平生用功甚专。得力最多。至是。又温习一过。常曰圣经贤传之旨。孰非治心之药石。然其语约而义精。功简而效博。体用俱该。本末兼备者。莫若此书云。○先是。修撰金万均。引祖母之雠。疏请不见北使。承旨徐必远启请还给其疏。至于拿罢。尤斋闻之。援朱子复雠尽五世之说。上章峻斥。徐公时为北伯投疏。自是以祖父母。为不入于三纲。于是一时论议转激。极意攻击。且谓今之立朝者。自高曾祖至从兄弟朋友之有雠者。皆当不见北人云。先生于诸公间。略以所尝泾渭者。明其不然。谤言因以大起。文谷金公寿恒。以书来问其由。先生答之。略曰。大槩凡有雠之之义者。一与彼人相见之后。更不可报。则上自五代祖。下至朋友之雠。皆不见可也。不然则有父母祖父母之雠者。固不忍见。其下则酌其轻重。为一定制。恐不得不已。盖父母祖父母。则私恩为重。公义为轻。自从兄弟以下。则私恩为轻。公义为重。虽不可无必报其雠之心。亦不可不隐忍而与彼相接也。父母与祖父母之间。谓无分毫之差。则人情天理。恐不必如此。朱夫子亦有自是稍轻之训。然虽有分毫之差。而便同一科可也。北伯
▣▣▣▣▣▣▣▣除宗簿寺正。○三月。拜司谏。○四月。拜应教。○子贺朝生。○出寓东湖书堂。读心经。(先生尊信心经。笃好而深悦之。平生用功甚专。得力最多。至是。又温习一过。常曰圣经贤传之旨。孰非治心之药石。然其语约而义精。功简而效博。体用俱该。本末兼备者。莫若此书云。○先是。修撰金万均。引祖母之雠。疏请不见北使。承旨徐必远启请还给其疏。至于拿罢。尤斋闻之。援朱子复雠尽五世之说。上章峻斥。徐公时为北伯投疏。自是以祖父母。为不入于三纲。于是一时论议转激。极意攻击。且谓今之立朝者。自高曾祖至从兄弟朋友之有雠者。皆当不见北人云。先生于诸公间。略以所尝泾渭者。明其不然。谤言因以大起。文谷金公寿恒。以书来问其由。先生答之。略曰。大槩凡有雠之之义者。一与彼人相见之后。更不可报。则上自五代祖。下至朋友之雠。皆不见可也。不然则有父母祖父母之雠者。固不忍见。其下则酌其轻重。为一定制。恐不得不已。盖父母祖父母。则私恩为重。公义为轻。自从兄弟以下。则私恩为轻。公义为重。虽不可无必报其雠之心。亦不可不隐忍而与彼相接也。父母与祖父母之间。谓无分毫之差。则人情天理。恐不必如此。朱夫子亦有自是稍轻之训。然虽有分毫之差。而便同一科可也。北伯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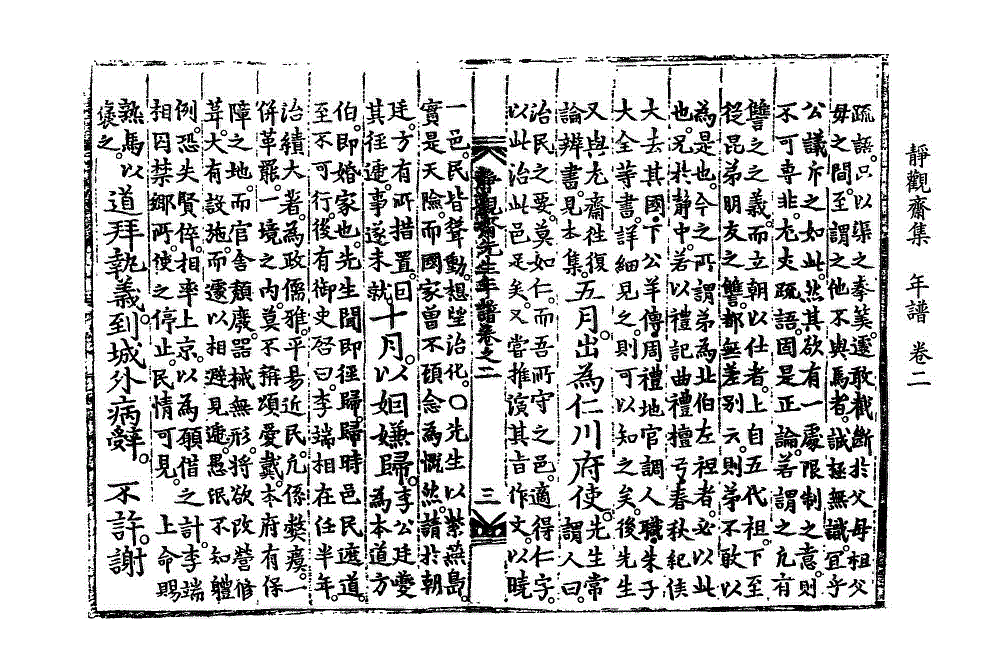 疏语。只以渠之拳算。遽敢截断于父母祖父母之间。至谓之他不与焉者。诚极无识。宜乎公议斥之如此。然其欲有一处限制之意。则不可专非。尤丈疏语。固是正论。若谓之凡有雠之之义。而立朝以仕者。上自五代祖。下至从昆弟朋友之雠。都无差别云。则弟不敢以为是也。今之所谓弟为北伯左袒者。必以此也。兄于静中。若以礼记曲礼檀弓,春秋纪侯大去其国,下公羊传,周礼地官调人职,朱子大全等书。详细见之。则可以知之矣。后先生又与尤斋往复论辨书。见本集。)五月。出为仁川府使。(先生常谓人曰。治民之要。莫如仁。而吾所守之邑。适得仁字。以此治此邑足矣。又尝推演其旨作文。以晓一邑。民皆耸动。想望治化。○先生以紫燕岛。实是天险。而国家曾不顿念为慨然。请于朝廷。方有所措置。因其径递。事遂未就。)十月。以姻嫌归。(李公廷夔为本道方伯。即婚家也。先生闻即径归。归时邑民遮道。至不可行。后有御史启曰。李端相在任半年。治绩大著。为政儒雅。平易近民。凡系弊瘼。一并革罢。一境之内。莫不称颂爱戴。本府有保障之地。而官舍颓废。器械无形。将欲改营修葺。大有设施。而遽以相避见递。愚氓不知体例。恐失贤倅。相率上京。以为愿借之计。李端相囚禁乡所。使之停止。民情可见。 上命赐熟马以褒之。)道拜执义。到城外病辞。 不许。谢
疏语。只以渠之拳算。遽敢截断于父母祖父母之间。至谓之他不与焉者。诚极无识。宜乎公议斥之如此。然其欲有一处限制之意。则不可专非。尤丈疏语。固是正论。若谓之凡有雠之之义。而立朝以仕者。上自五代祖。下至从昆弟朋友之雠。都无差别云。则弟不敢以为是也。今之所谓弟为北伯左袒者。必以此也。兄于静中。若以礼记曲礼檀弓,春秋纪侯大去其国,下公羊传,周礼地官调人职,朱子大全等书。详细见之。则可以知之矣。后先生又与尤斋往复论辨书。见本集。)五月。出为仁川府使。(先生常谓人曰。治民之要。莫如仁。而吾所守之邑。适得仁字。以此治此邑足矣。又尝推演其旨作文。以晓一邑。民皆耸动。想望治化。○先生以紫燕岛。实是天险。而国家曾不顿念为慨然。请于朝廷。方有所措置。因其径递。事遂未就。)十月。以姻嫌归。(李公廷夔为本道方伯。即婚家也。先生闻即径归。归时邑民遮道。至不可行。后有御史启曰。李端相在任半年。治绩大著。为政儒雅。平易近民。凡系弊瘼。一并革罢。一境之内。莫不称颂爱戴。本府有保障之地。而官舍颓废。器械无形。将欲改营修葺。大有设施。而遽以相避见递。愚氓不知体例。恐失贤倅。相率上京。以为愿借之计。李端相囚禁乡所。使之停止。民情可见。 上命赐熟马以褒之。)道拜执义。到城外病辞。 不许。谢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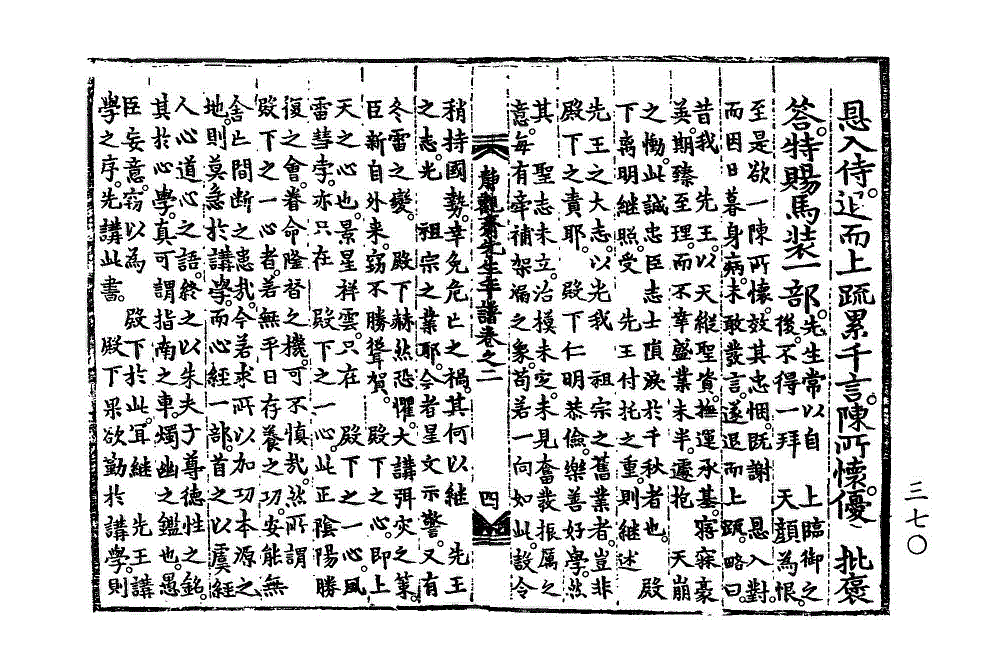 恩入侍。退而上疏累千言。陈所怀。优 批褒答。特赐马装一部。(先生常以自 上临御之后。不得一拜 天颜为恨。至是欲一陈所怀。效其忠悃。既谢 恩入对。而因日暮身病。未敢发言。遂退而上疏。略曰。昔我 先王。以天纵圣资。抚运承基。寤寐豪英。期臻至理。而不幸盛业未半。遽抱 天崩之恸。此诚忠臣志士陨泪于千秋者也。 殿下离明继照。受 先王付托之重。则继述 先王之大志。以光我 祖宗之旧业者。岂非殿下之责耶。 殿下仁明恭俭。乐善好学。然其 圣志未立。治模未定。未见奋发振厉之意。每有牵补架漏之象。苟若一向如此。设令稍持国势。幸免危亡之祸。其何以继 先王之志。光 祖宗之业耶。今者星文示警。又有冬雷之变。 殿下赫然恐惧。大讲弭灾之策。臣新自外来。窃不胜耸贺。 殿下之心。即上天之心也。景星祥云。只在 殿下之一心。风雷彗孛。亦只在 殿下之一心。此正阴阳胜复之会。眷命隆替之机。可不慎哉。然所谓 殿下之一心者。若无平日存养之功。安能无舍亡间断之患哉。今若求所以加功本源之地。则莫急于讲学。而心经一部。首之以虞经人心道心之语。终之以朱夫子尊德性之铭。其于心学。真可谓指南之车。烛幽之鉴也。愚臣妄意。窃以为 殿下于此。宜继 先王讲学之序。先讲此书。 殿下果欲勤于讲学。则
恩入侍。退而上疏累千言。陈所怀。优 批褒答。特赐马装一部。(先生常以自 上临御之后。不得一拜 天颜为恨。至是欲一陈所怀。效其忠悃。既谢 恩入对。而因日暮身病。未敢发言。遂退而上疏。略曰。昔我 先王。以天纵圣资。抚运承基。寤寐豪英。期臻至理。而不幸盛业未半。遽抱 天崩之恸。此诚忠臣志士陨泪于千秋者也。 殿下离明继照。受 先王付托之重。则继述 先王之大志。以光我 祖宗之旧业者。岂非殿下之责耶。 殿下仁明恭俭。乐善好学。然其 圣志未立。治模未定。未见奋发振厉之意。每有牵补架漏之象。苟若一向如此。设令稍持国势。幸免危亡之祸。其何以继 先王之志。光 祖宗之业耶。今者星文示警。又有冬雷之变。 殿下赫然恐惧。大讲弭灾之策。臣新自外来。窃不胜耸贺。 殿下之心。即上天之心也。景星祥云。只在 殿下之一心。风雷彗孛。亦只在 殿下之一心。此正阴阳胜复之会。眷命隆替之机。可不慎哉。然所谓 殿下之一心者。若无平日存养之功。安能无舍亡间断之患哉。今若求所以加功本源之地。则莫急于讲学。而心经一部。首之以虞经人心道心之语。终之以朱夫子尊德性之铭。其于心学。真可谓指南之车。烛幽之鉴也。愚臣妄意。窃以为 殿下于此。宜继 先王讲学之序。先讲此书。 殿下果欲勤于讲学。则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1H 页
 必先保养 圣躬。而年来 玉候常多违豫之日。中外臣民。非无隐虑于中者。畏慑趑趄。不敢仰陈。人主一身。处亿兆之上。居九重之内。意之所向。谁复止遏。而左右前后。无非女御。则在色之戒。倍难于平人。强制之难。不独曲蘖而已。 殿下果能保养 圣躬。勤于讲学。则不可不先致草野之贤。而至若宋时烈,宋浚吉等。则岂但以讲学而招延而已也。今此两臣。身任大义。出处进退。惟义是视。所谓大义大志者。岂必明言倡说。徒烦听闻。而后始可以召致两臣也。天运回环。自有其时。无实效而受实祸。是 先王之所大讳也。今 殿下若常存此心。念念不忘。而至诚虚伫。频降 召命。或遣史官。或遣承旨。一召不来。再召之。再召不来。三召之。以至四五召六七召而不已。则时烈,浚吉。本非无意于世者。岂不思追先帝之殊遇。以报之于陛下之义耶。顷年。时烈以意外之事。苍黄退去。又以服制议礼之事。有善道之疏。其后赵絅,洪宇远,赵寿益等诸人之疏。相继而起。及至顷日。又以金万均之事。遽有徐必远之疏。必远之断自祖孙者。果为无识。而其所谓不可无斟量云者。则不可谓全无所见。然其以粗厉之语。肆加讥侮于时烈者。极涉骇悖。乌得无罪。而前后之攻必远者。攻之太深。亦未能得其情而使自愧服。 殿下于其间。时有显示左右者。时烈之不安。势亦然矣。此外又有一事。举国中外。莫不知之。而独 殿下未之知耳。臣何忍
必先保养 圣躬。而年来 玉候常多违豫之日。中外臣民。非无隐虑于中者。畏慑趑趄。不敢仰陈。人主一身。处亿兆之上。居九重之内。意之所向。谁复止遏。而左右前后。无非女御。则在色之戒。倍难于平人。强制之难。不独曲蘖而已。 殿下果能保养 圣躬。勤于讲学。则不可不先致草野之贤。而至若宋时烈,宋浚吉等。则岂但以讲学而招延而已也。今此两臣。身任大义。出处进退。惟义是视。所谓大义大志者。岂必明言倡说。徒烦听闻。而后始可以召致两臣也。天运回环。自有其时。无实效而受实祸。是 先王之所大讳也。今 殿下若常存此心。念念不忘。而至诚虚伫。频降 召命。或遣史官。或遣承旨。一召不来。再召之。再召不来。三召之。以至四五召六七召而不已。则时烈,浚吉。本非无意于世者。岂不思追先帝之殊遇。以报之于陛下之义耶。顷年。时烈以意外之事。苍黄退去。又以服制议礼之事。有善道之疏。其后赵絅,洪宇远,赵寿益等诸人之疏。相继而起。及至顷日。又以金万均之事。遽有徐必远之疏。必远之断自祖孙者。果为无识。而其所谓不可无斟量云者。则不可谓全无所见。然其以粗厉之语。肆加讥侮于时烈者。极涉骇悖。乌得无罪。而前后之攻必远者。攻之太深。亦未能得其情而使自愧服。 殿下于其间。时有显示左右者。时烈之不安。势亦然矣。此外又有一事。举国中外。莫不知之。而独 殿下未之知耳。臣何忍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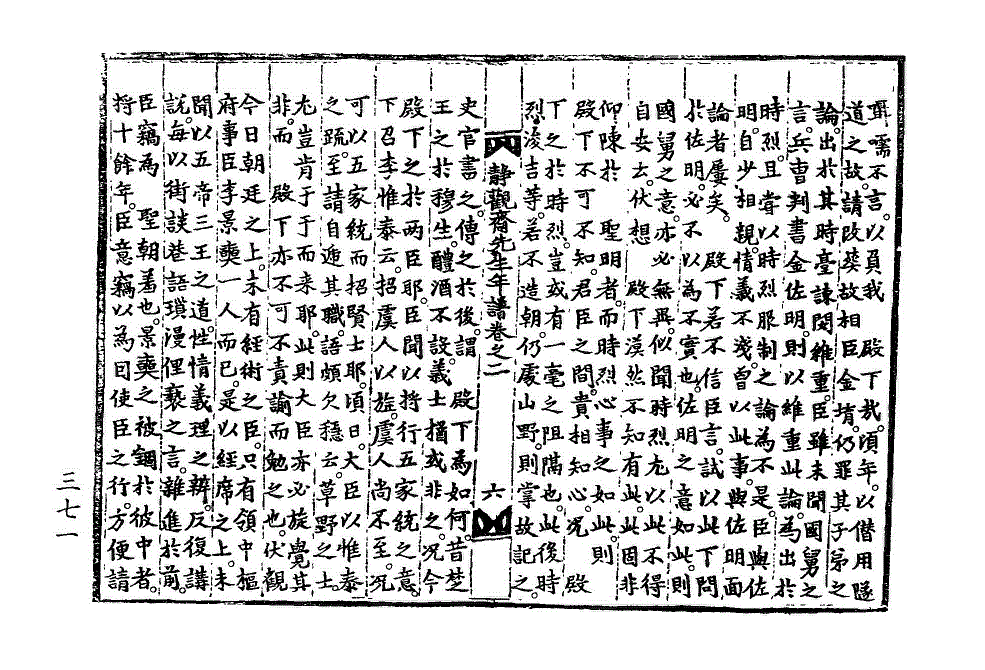 嗫嚅不言。以负我 殿下哉。顷年。以僭用隧道之故。请改葬故相臣金堉。仍罪其子弟之论。出于其时台谏闵维重。臣虽未闻国舅之言。兵曹判书金佐明。则以维重此论。为出于时烈。且尝以时烈服制之论为不是。臣与佐明。自少相亲。情义不浅。曾以此事。与佐明面论者屡矣。 殿下若不信臣言。试以此下问于佐明。必不以为不实也。佐明之意如此。则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似闻时烈尤以此不得自安云。伏想 殿下漠然不知有此。此固非仰陈于 圣明者。而时烈心事之如此。则 殿下不可不知。君臣之间。贵相知心。况 殿下之于时烈。岂或有一毫之阻隔也。此后时烈,浚吉等。若不造朝。仍处山野。则掌故记之。史官书之。传之于后。谓 殿下为如何。昔楚王之于穆生。醴酒不设。义士犹或非之。况今殿下之于两臣耶。臣闻以将行五家统之意。下召李惟泰云。招虞人以旌。虞人尚不至。况可以五家统而招贤士耶。顷日。大臣以惟泰之疏。至请自递其职。语颇欠稳云。草野之士。尤岂肯于于而来耶。此则大臣亦必旋觉其非。而 殿下亦不可不责谕而勉之也。伏观今日朝廷之上。未有经术之臣。只有领中枢府事臣李景奭一人而已。是以经席之上。未闻以五帝三王之道。性情义理之辨。反复讲说。每以街谈巷语琐漫俚亵之言。杂进于前。臣窃为 圣朝羞也。景奭之被锢于彼中者。将十馀年。臣意窃以为因使臣之行。方便请
嗫嚅不言。以负我 殿下哉。顷年。以僭用隧道之故。请改葬故相臣金堉。仍罪其子弟之论。出于其时台谏闵维重。臣虽未闻国舅之言。兵曹判书金佐明。则以维重此论。为出于时烈。且尝以时烈服制之论为不是。臣与佐明。自少相亲。情义不浅。曾以此事。与佐明面论者屡矣。 殿下若不信臣言。试以此下问于佐明。必不以为不实也。佐明之意如此。则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似闻时烈尤以此不得自安云。伏想 殿下漠然不知有此。此固非仰陈于 圣明者。而时烈心事之如此。则 殿下不可不知。君臣之间。贵相知心。况 殿下之于时烈。岂或有一毫之阻隔也。此后时烈,浚吉等。若不造朝。仍处山野。则掌故记之。史官书之。传之于后。谓 殿下为如何。昔楚王之于穆生。醴酒不设。义士犹或非之。况今殿下之于两臣耶。臣闻以将行五家统之意。下召李惟泰云。招虞人以旌。虞人尚不至。况可以五家统而招贤士耶。顷日。大臣以惟泰之疏。至请自递其职。语颇欠稳云。草野之士。尤岂肯于于而来耶。此则大臣亦必旋觉其非。而 殿下亦不可不责谕而勉之也。伏观今日朝廷之上。未有经术之臣。只有领中枢府事臣李景奭一人而已。是以经席之上。未闻以五帝三王之道。性情义理之辨。反复讲说。每以街谈巷语琐漫俚亵之言。杂进于前。臣窃为 圣朝羞也。景奭之被锢于彼中者。将十馀年。臣意窃以为因使臣之行。方便请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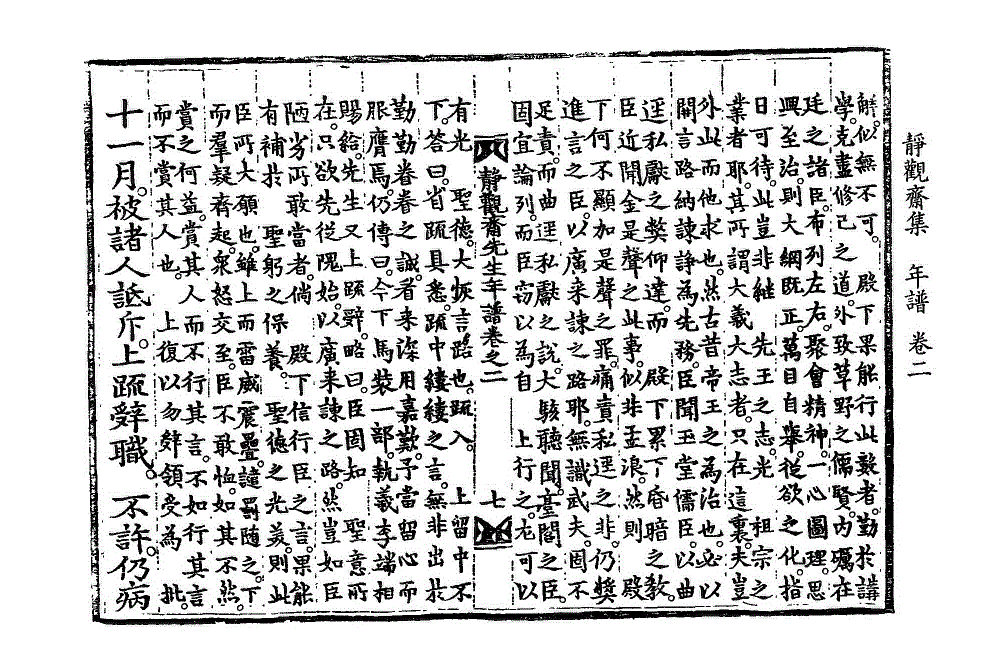 解。似无不可。 殿下果能行此数者。勤于讲学。克尽修己之道。外致草野之儒贤。内砺在廷之诸臣。布列左右。聚会精神。一心图理。思兴至治。则大纲既正。万目自举。从欲之化。指日可待。此岂非继 先王之志。光 祖宗之业者耶。其所谓大义大志者。只在这里。夫岂外此而他求也。然古昔帝王之为治也。必以开言路纳谏诤为先务。臣闻玉堂儒臣。以曲径私献之弊仰达。而 殿下累下昏暗之教。臣近闻金是声之此事。似非孟浪。然则 殿下何不显加是声之罪。痛责私径之非。仍奖进言之臣。以广来谏之路耶。无识武夫。固不足责。而曲径私献之说。大骇听闻。台阁之臣。固宜论列。而臣窃以为自 上行之。尤可以有光 圣德。大恢言路也。疏入。 上留中不下。答曰。省疏具悉。疏中缕缕之言。无非出于勤勤眷眷之诚。看来深用嘉叹。予当留心而服膺焉。仍传曰。今下马装一部。执义李端相赐给。先生又上疏辞。略曰。臣固知 圣意所在。只欲先从隗始。以广来谏之路。然岂如臣陋劣所敢当者。倘 殿下信行臣之言。果能有补于 圣躬之保养。 圣德之光美。则此臣所大愿也。虽上而雷威震叠。谴罚随之。下而群疑齐起。众怒交至。臣不敢恤。如其不然。赏之何益。赏其人而不行其言。不如行其言而不赏其人也。 上复以勿辞领受为 批。)十一月。被诸人诋斥。上疏辞职。 不许。仍病
解。似无不可。 殿下果能行此数者。勤于讲学。克尽修己之道。外致草野之儒贤。内砺在廷之诸臣。布列左右。聚会精神。一心图理。思兴至治。则大纲既正。万目自举。从欲之化。指日可待。此岂非继 先王之志。光 祖宗之业者耶。其所谓大义大志者。只在这里。夫岂外此而他求也。然古昔帝王之为治也。必以开言路纳谏诤为先务。臣闻玉堂儒臣。以曲径私献之弊仰达。而 殿下累下昏暗之教。臣近闻金是声之此事。似非孟浪。然则 殿下何不显加是声之罪。痛责私径之非。仍奖进言之臣。以广来谏之路耶。无识武夫。固不足责。而曲径私献之说。大骇听闻。台阁之臣。固宜论列。而臣窃以为自 上行之。尤可以有光 圣德。大恢言路也。疏入。 上留中不下。答曰。省疏具悉。疏中缕缕之言。无非出于勤勤眷眷之诚。看来深用嘉叹。予当留心而服膺焉。仍传曰。今下马装一部。执义李端相赐给。先生又上疏辞。略曰。臣固知 圣意所在。只欲先从隗始。以广来谏之路。然岂如臣陋劣所敢当者。倘 殿下信行臣之言。果能有补于 圣躬之保养。 圣德之光美。则此臣所大愿也。虽上而雷威震叠。谴罚随之。下而群疑齐起。众怒交至。臣不敢恤。如其不然。赏之何益。赏其人而不行其言。不如行其言而不赏其人也。 上复以勿辞领受为 批。)十一月。被诸人诋斥。上疏辞职。 不许。仍病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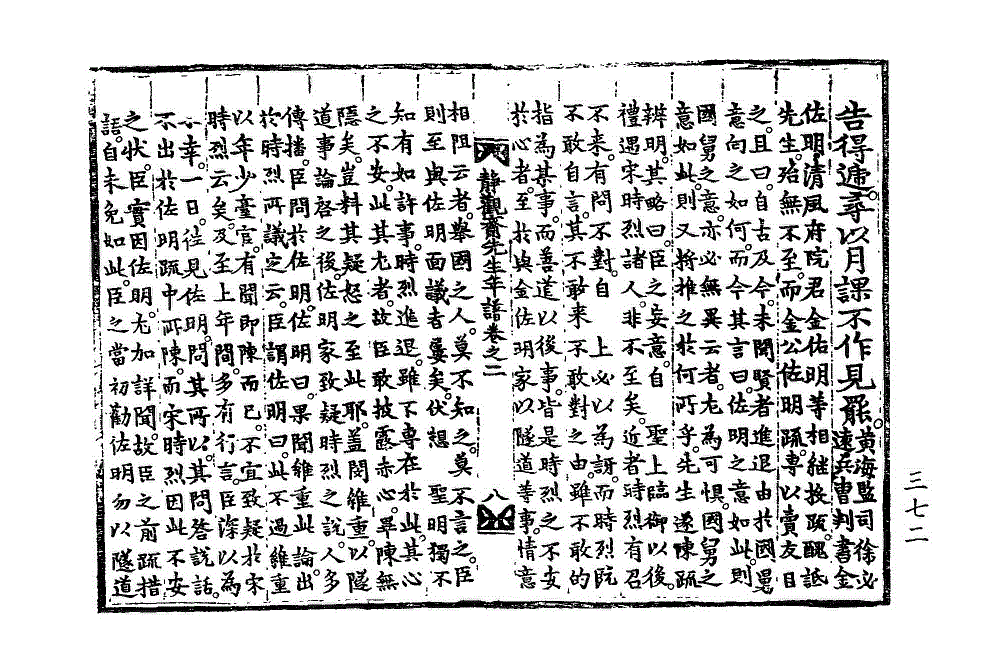 告得递。寻以月课不作见罢。(黄海监司徐必远兵曹判书金佐明,清风府院君金佑明等相继投疏。丑诋先生。殆无不至。而金公佐明疏。专以卖友目之。且曰。自古及今。未闻贤者进退由于国舅意向之如何。而今其言曰。佐明之意如此。则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云者。尤为可惧。国舅之意如此。则又将推之于何所乎。先生遂陈疏辨明。其略曰。臣之妄意。自 圣上临御以后。礼遇宋时烈诸人。非不至矣。近者时烈有召不来。有问不对。自 上必以为讶。而时烈既不敢自言。其不敢来不敢对之由。虽不敢的指为某事。而善道以后事。皆是时烈之不安于心者。至于与金佐明家以隧道等事。情意相阻云者。举国之人。莫不知之。莫不言之。臣则至与佐明面议者屡矣。伏想 圣明独不知有如许事。时烈进退。虽不专在于此。其心之不安。此其尤者。故臣敢披露赤心。毕陈无隐矣。岂料其疑怒之至此耶。盖闵维重。以隧道事论启之后。佐明家致疑时烈之说。人多传播。臣问于佐明。佐明曰。果闻维重此论。出于时烈所议定云。臣谓佐明曰。此不过维重以年少台官。有闻即陈而已。不宜致疑于宋时烈云矣。及至上年间。多有行言。臣深以为不幸。一日。往见佐明。问其所以。其问答说话。不出于佐明疏中所陈。而宋时烈因此不安之状。臣实因佐明。尤加详闻。故臣之前疏措语。自未免如此。臣之当初劝佐明勿以隧道
告得递。寻以月课不作见罢。(黄海监司徐必远兵曹判书金佐明,清风府院君金佑明等相继投疏。丑诋先生。殆无不至。而金公佐明疏。专以卖友目之。且曰。自古及今。未闻贤者进退由于国舅意向之如何。而今其言曰。佐明之意如此。则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云者。尤为可惧。国舅之意如此。则又将推之于何所乎。先生遂陈疏辨明。其略曰。臣之妄意。自 圣上临御以后。礼遇宋时烈诸人。非不至矣。近者时烈有召不来。有问不对。自 上必以为讶。而时烈既不敢自言。其不敢来不敢对之由。虽不敢的指为某事。而善道以后事。皆是时烈之不安于心者。至于与金佐明家以隧道等事。情意相阻云者。举国之人。莫不知之。莫不言之。臣则至与佐明面议者屡矣。伏想 圣明独不知有如许事。时烈进退。虽不专在于此。其心之不安。此其尤者。故臣敢披露赤心。毕陈无隐矣。岂料其疑怒之至此耶。盖闵维重。以隧道事论启之后。佐明家致疑时烈之说。人多传播。臣问于佐明。佐明曰。果闻维重此论。出于时烈所议定云。臣谓佐明曰。此不过维重以年少台官。有闻即陈而已。不宜致疑于宋时烈云矣。及至上年间。多有行言。臣深以为不幸。一日。往见佐明。问其所以。其问答说话。不出于佐明疏中所陈。而宋时烈因此不安之状。臣实因佐明。尤加详闻。故臣之前疏措语。自未免如此。臣之当初劝佐明勿以隧道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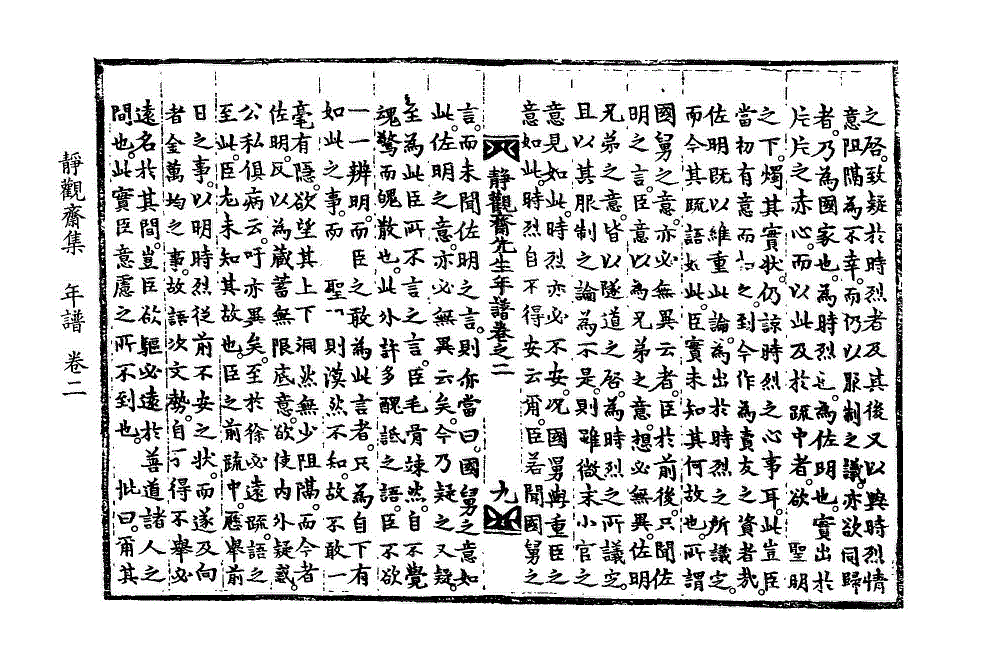 之启。致疑于时烈者及其后又以与时烈情意阻隔为不幸。而仍以服制之议。亦欲同归者。乃为国家也。为时烈也。为佐明也。实出于片片之赤心。而以此及于疏中者。欲 圣明之下。烛其实状。仍谅时烈之心事耳。此岂臣当初有意而▦之。到今作为卖友之资者哉。佐明既以维重此论。为出于时烈之所议定。而今其疏语如此。臣实未知其何故也。所谓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云者。臣于前后。只闻佐明之言。臣意以为兄弟之意。想必无异。佐明兄弟之意。皆以隧道之启。为时烈之所议定。且以其服制之论为不是。则虽微末小官之意见如此。时烈亦必不安。况国舅与重臣之意如此。时烈自不得安云尔。臣若闻国舅之言。而未闻佐明之言。则亦当曰。国舅之意如此。佐明之意。亦必无异云矣。今乃疑之又疑。至为此臣所不言之言。臣毛骨竦然。自不觉魂惊而魄散也。此外许多丑诋之语。臣不欲一一辨明。而臣之敢为此言者。只为自下有如此之事。而 圣明则漠然不知。故不敢一毫有隐。欲望其上下洞然无少阻隔。而今者佐明。反以为藏蓄无限底意。欲使内外疑惑。公私俱病云。吁亦异矣。至于徐必远疏。语之至此。臣尤未知其故也。臣之前疏中。历举前日之事。以明时烈从前不安之状。而遂及向者金万均之事。故语次文势。自不得不举必远名于其间。岂臣欲驱必远于善道诸人之间也。此实臣意虑之所不到也。 批曰。尔其
之启。致疑于时烈者及其后又以与时烈情意阻隔为不幸。而仍以服制之议。亦欲同归者。乃为国家也。为时烈也。为佐明也。实出于片片之赤心。而以此及于疏中者。欲 圣明之下。烛其实状。仍谅时烈之心事耳。此岂臣当初有意而▦之。到今作为卖友之资者哉。佐明既以维重此论。为出于时烈之所议定。而今其疏语如此。臣实未知其何故也。所谓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云者。臣于前后。只闻佐明之言。臣意以为兄弟之意。想必无异。佐明兄弟之意。皆以隧道之启。为时烈之所议定。且以其服制之论为不是。则虽微末小官之意见如此。时烈亦必不安。况国舅与重臣之意如此。时烈自不得安云尔。臣若闻国舅之言。而未闻佐明之言。则亦当曰。国舅之意如此。佐明之意。亦必无异云矣。今乃疑之又疑。至为此臣所不言之言。臣毛骨竦然。自不觉魂惊而魄散也。此外许多丑诋之语。臣不欲一一辨明。而臣之敢为此言者。只为自下有如此之事。而 圣明则漠然不知。故不敢一毫有隐。欲望其上下洞然无少阻隔。而今者佐明。反以为藏蓄无限底意。欲使内外疑惑。公私俱病云。吁亦异矣。至于徐必远疏。语之至此。臣尤未知其故也。臣之前疏中。历举前日之事。以明时烈从前不安之状。而遂及向者金万均之事。故语次文势。自不得不举必远名于其间。岂臣欲驱必远于善道诸人之间也。此实臣意虑之所不到也。 批曰。尔其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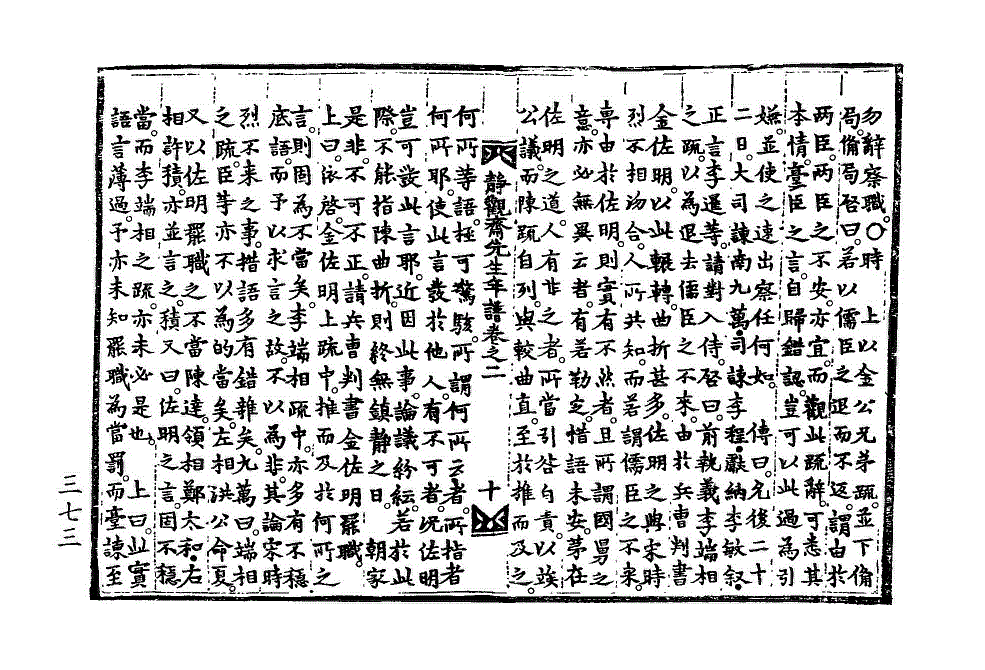 勿辞察职。○时 上以金公兄弟疏。并下备局。备局启曰。若以儒臣之退而不返。谓由于两臣。两臣之不安。亦宜。而观此疏辞。可悉其本情。台臣之言。自归错认。岂可以此过为引嫌。并使之速出察任何如。 传曰。允后二十二日。大司谏南九万,司谏李程,献纳李敏叙,正言李暹等。请对入侍。启曰。前执义李端相之疏。以为退去儒臣之不来。由于兵曹判书金佐明。以此辗转。曲折甚多。佐明之与宋时烈不相沕合。人所共知。而若谓儒臣之不来。专由于佐明。则实有不然者。旦所谓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云者。有若勒定。惜语未安。第在佐明之道。人有非之者。所当引咎自责。以俟公议。而陈疏自列。与较曲直。至于推而及之。何所等语。极可惊骇。所谓何所云者。所指者何所耶。使此言发于他人。有不可者。况佐明岂可发此言耶。近因此事。论议纷纭。若于此际。不能指陈曲折。则终无镇静之日。 朝家是非。不可不正。请兵曹判书金佐明罢职。 上曰。依启。金佐明上疏中。推而及于何所之言。则固为不当矣。李端相疏中。亦多有不稳底语。而予以求言之故。不以为非。其论宋时烈不来之事。措语多有错杂矣。九万曰。端相之疏。臣等亦不以为的当矣。左相洪公命夏。又以佐明罢职之不当陈达。领相郑太和,右相许积。亦并言之。积又曰。佐明之言。固不稳当。而李端相之疏。亦未必是也。 上曰。此实语言薄过。予亦未知罢职为当罚。而台谏至
勿辞察职。○时 上以金公兄弟疏。并下备局。备局启曰。若以儒臣之退而不返。谓由于两臣。两臣之不安。亦宜。而观此疏辞。可悉其本情。台臣之言。自归错认。岂可以此过为引嫌。并使之速出察任何如。 传曰。允后二十二日。大司谏南九万,司谏李程,献纳李敏叙,正言李暹等。请对入侍。启曰。前执义李端相之疏。以为退去儒臣之不来。由于兵曹判书金佐明。以此辗转。曲折甚多。佐明之与宋时烈不相沕合。人所共知。而若谓儒臣之不来。专由于佐明。则实有不然者。旦所谓国舅之意。亦必无异云者。有若勒定。惜语未安。第在佐明之道。人有非之者。所当引咎自责。以俟公议。而陈疏自列。与较曲直。至于推而及之。何所等语。极可惊骇。所谓何所云者。所指者何所耶。使此言发于他人。有不可者。况佐明岂可发此言耶。近因此事。论议纷纭。若于此际。不能指陈曲折。则终无镇静之日。 朝家是非。不可不正。请兵曹判书金佐明罢职。 上曰。依启。金佐明上疏中。推而及于何所之言。则固为不当矣。李端相疏中。亦多有不稳底语。而予以求言之故。不以为非。其论宋时烈不来之事。措语多有错杂矣。九万曰。端相之疏。臣等亦不以为的当矣。左相洪公命夏。又以佐明罢职之不当陈达。领相郑太和,右相许积。亦并言之。积又曰。佐明之言。固不稳当。而李端相之疏。亦未必是也。 上曰。此实语言薄过。予亦未知罢职为当罚。而台谏至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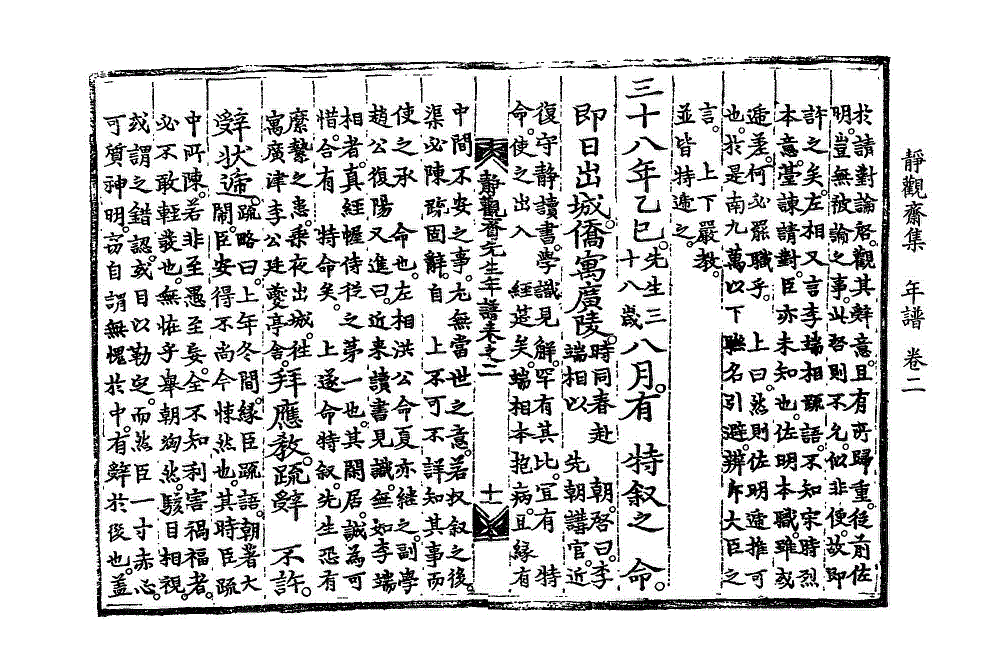 于请对论启。观其辞意。且有所归重。从前佐明。岂无被论之事。此启则不允。似非便。故即许之矣。左相又言李端相疏语。不知宋时烈本意。台谏请对。臣亦未知也。佐明本职。虽或递差。何必罢职乎。 上曰。然则佐明递推可也。于是南九万以下联名引避。辨斥大臣之言。 上下严教。并皆特递之。)
于请对论启。观其辞意。且有所归重。从前佐明。岂无被论之事。此启则不允。似非便。故即许之矣。左相又言李端相疏语。不知宋时烈本意。台谏请对。臣亦未知也。佐明本职。虽或递差。何必罢职乎。 上曰。然则佐明递推可也。于是南九万以下联名引避。辨斥大臣之言。 上下严教。并皆特递之。)三十八年乙巳。(先生三十八岁)八月。有 特叙之 命。即日出城。侨寓广陵。(时同春赴 朝。启曰。李端相以 先朝讲官。近复守静读书。学识见解。罕有其比。宜有 特命。使之出入 经筵矣。端相本抱病。且缘有中间不安之事。尤无当世之意。若收叙之后。渠必陈疏固辞。自 上不可不详知其事而使之承 命也。左相洪公命夏亦继之。副学赵公复阳又进曰。近来读书见识。无如李端相者。真经幄侍从之第一也。其闲居。诚为可惜。合有 特命矣。 上遂命特叙。先生恐有縻絷之患。乘夜出城。往寓广津李公廷夔亭舍。)拜应教。疏辞 不许。辞状递。(疏略曰。上年冬间。缘臣疏语。朝著大闹。臣安得不尚今悚然也。其时臣疏中所陈。若非至愚至妄。全不知利害祸福者。必不敢轻发也。无怪乎举朝汹然。骇目相视。或谓之错认。或目以勒定。而然臣一寸赤心。可质神明。窃自谓无愧于中。有辞于后也。盖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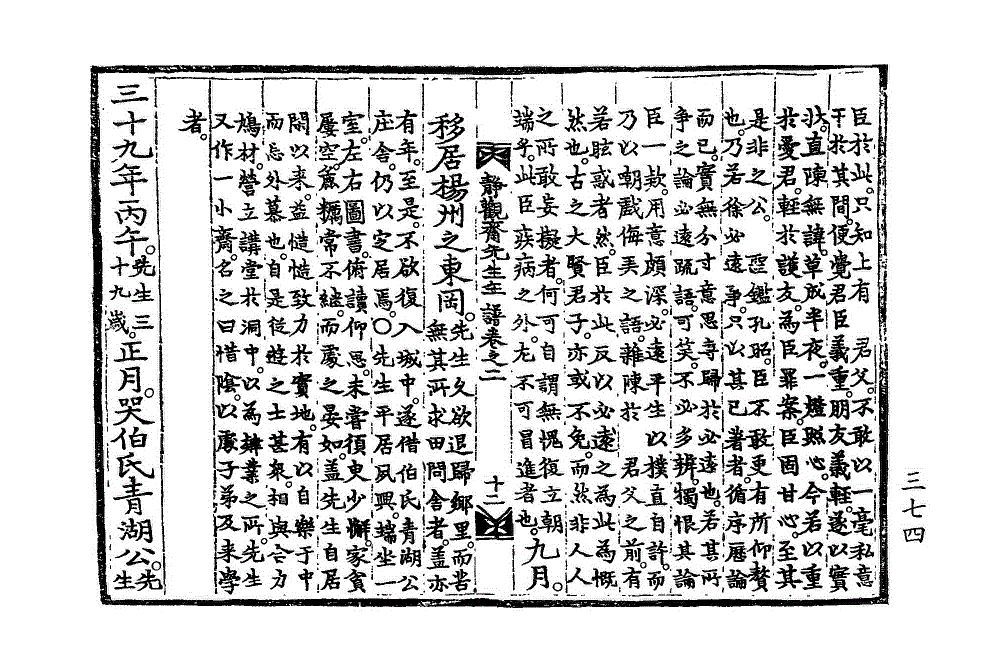 臣于此。只知上有 君父。不敢以一毫私意干于其间。便觉君臣义重。朋友义轻。遂以实状。直陈无讳。草成半夜。一灯照心。今若以重于爱君。轻于护友。为臣罪案。臣固甘心。至其是非之公。 圣鉴孔昭。臣不敢更有所仰赘也。乃若徐必远事。只以其已著者。循序历论而已。实无分思寸意专归于必远也。若其所争之论必远疏语。可笑。不必多辨。独恨其论臣一款。用意颇深。必远平生以朴直自许。而乃以嘲戏侮弄之语。杂陈于 君父之前。有若眩惑者然。臣于此反以必远之为此为慨然也。古之大贤君子。亦或不免。而然非人人之所敢妄拟者。何可自谓无愧复立朝端乎。此臣疾病之外。尤不可冒进者也。)九月。移居杨州之东冈。(先生久欲退归乡里。而苦无其所求田问舍者。盖亦有年。至是。不欲复入城中。遂借伯氏青湖公庄舍。仍以定居焉。○先生平居夙兴。端坐一室。左右图书。俯读仰思。未尝须臾少懈。家贫屡空。粗粝常不继。而处之晏如。盖先生自居闲以来。益慥慥致力于实地。有以自乐于中而忘外慕也。自是从游之士甚众。相与合力鸠材。营立讲堂于洞中。以为肄业之所。先生又作一小斋。之曰名惜阴。以处子弟及来学者。)
臣于此。只知上有 君父。不敢以一毫私意干于其间。便觉君臣义重。朋友义轻。遂以实状。直陈无讳。草成半夜。一灯照心。今若以重于爱君。轻于护友。为臣罪案。臣固甘心。至其是非之公。 圣鉴孔昭。臣不敢更有所仰赘也。乃若徐必远事。只以其已著者。循序历论而已。实无分思寸意专归于必远也。若其所争之论必远疏语。可笑。不必多辨。独恨其论臣一款。用意颇深。必远平生以朴直自许。而乃以嘲戏侮弄之语。杂陈于 君父之前。有若眩惑者然。臣于此反以必远之为此为慨然也。古之大贤君子。亦或不免。而然非人人之所敢妄拟者。何可自谓无愧复立朝端乎。此臣疾病之外。尤不可冒进者也。)九月。移居杨州之东冈。(先生久欲退归乡里。而苦无其所求田问舍者。盖亦有年。至是。不欲复入城中。遂借伯氏青湖公庄舍。仍以定居焉。○先生平居夙兴。端坐一室。左右图书。俯读仰思。未尝须臾少懈。家贫屡空。粗粝常不继。而处之晏如。盖先生自居闲以来。益慥慥致力于实地。有以自乐于中而忘外慕也。自是从游之士甚众。相与合力鸠材。营立讲堂于洞中。以为肄业之所。先生又作一小斋。之曰名惜阴。以处子弟及来学者。)三十九年丙午。(先生三十九岁。)正月。哭伯氏青湖公。(先生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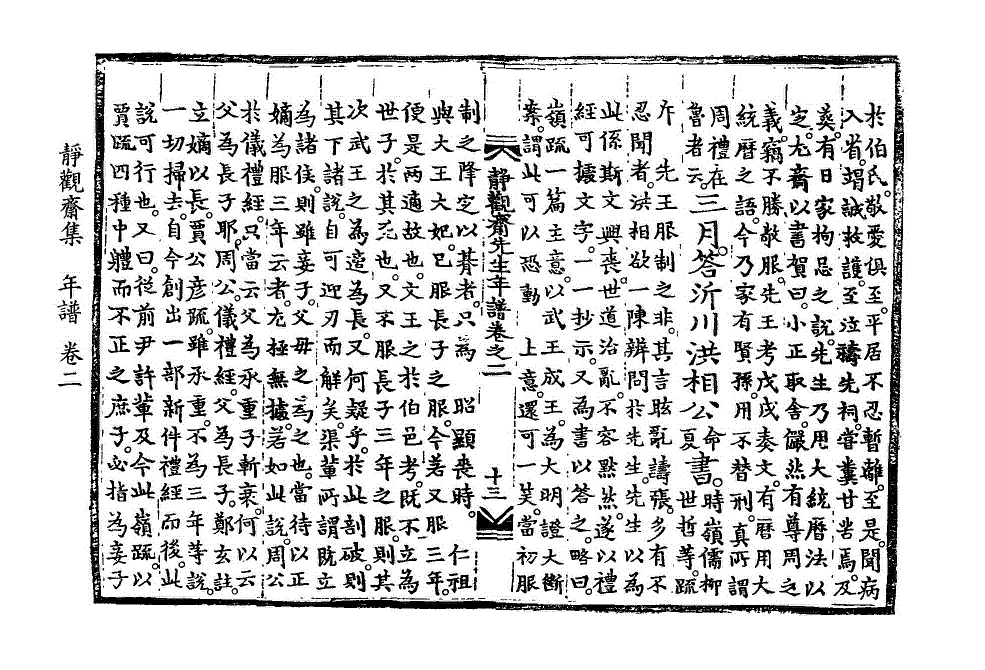 于伯氏。敬爱俱至。平居不忍暂离。至是。闻病入省。竭诚救护。至泣祷先祠。尝粪甘苦焉。及葬。有日家拘忌之说。先生乃用大统历法以定。尤斋以书贺曰。小正取舍。俨然有尊周之义。窃不胜敬服。先王考戊戌奏文。有历用大统历之语。今乃家有贤孙。用不替刑。真所谓周礼在鲁者云。)三月。答沂川洪相公(命夏)书。(时岭儒柳世哲等。疏斥 先王服制之非。其言眩乱诪张。多有不忍闻者。洪相欲一陈辨问于先生。生生以为此系斯文兴丧。世道治乱。不容默然。遂以礼经可据文字。一一抄示。又为书以答之。略曰。岭疏一篇主意。以武王成王。为大明證大断案。谓此可以恐动 上意。还可一笑。当初服制之降定以期者。只为 昭显丧时。 仁祖与大王大妃。已服长子之服。今若又服三年。便是两适故也。文王之于伯邑考。既不立为世子。于其死也。又不服长子三年之服。则其次武王之为适为长。又何疑乎。于此剖破。则其下诸说。自可迎刃而解矣。渠辈所谓既立为诸侯。则虽妾子。父母之为之也。当待以正嫡为服三年云者。尤极无据。若如此说。周公于仪礼经。只当云父为承重子斩衰。何以云父为长子耶。周公。仪礼经。父为长子。郑玄注。立嫡以长。贾公彦疏。虽承重。不为三年等说。一切扫去。自今创出一部新件礼经而后。此说可行也。又曰。从前尹许辈及今此岭疏。以贾疏四种中体而不正之庶子。必指为妾子
于伯氏。敬爱俱至。平居不忍暂离。至是。闻病入省。竭诚救护。至泣祷先祠。尝粪甘苦焉。及葬。有日家拘忌之说。先生乃用大统历法以定。尤斋以书贺曰。小正取舍。俨然有尊周之义。窃不胜敬服。先王考戊戌奏文。有历用大统历之语。今乃家有贤孙。用不替刑。真所谓周礼在鲁者云。)三月。答沂川洪相公(命夏)书。(时岭儒柳世哲等。疏斥 先王服制之非。其言眩乱诪张。多有不忍闻者。洪相欲一陈辨问于先生。生生以为此系斯文兴丧。世道治乱。不容默然。遂以礼经可据文字。一一抄示。又为书以答之。略曰。岭疏一篇主意。以武王成王。为大明證大断案。谓此可以恐动 上意。还可一笑。当初服制之降定以期者。只为 昭显丧时。 仁祖与大王大妃。已服长子之服。今若又服三年。便是两适故也。文王之于伯邑考。既不立为世子。于其死也。又不服长子三年之服。则其次武王之为适为长。又何疑乎。于此剖破。则其下诸说。自可迎刃而解矣。渠辈所谓既立为诸侯。则虽妾子。父母之为之也。当待以正嫡为服三年云者。尤极无据。若如此说。周公于仪礼经。只当云父为承重子斩衰。何以云父为长子耶。周公。仪礼经。父为长子。郑玄注。立嫡以长。贾公彦疏。虽承重。不为三年等说。一切扫去。自今创出一部新件礼经而后。此说可行也。又曰。从前尹许辈及今此岭疏。以贾疏四种中体而不正之庶子。必指为妾子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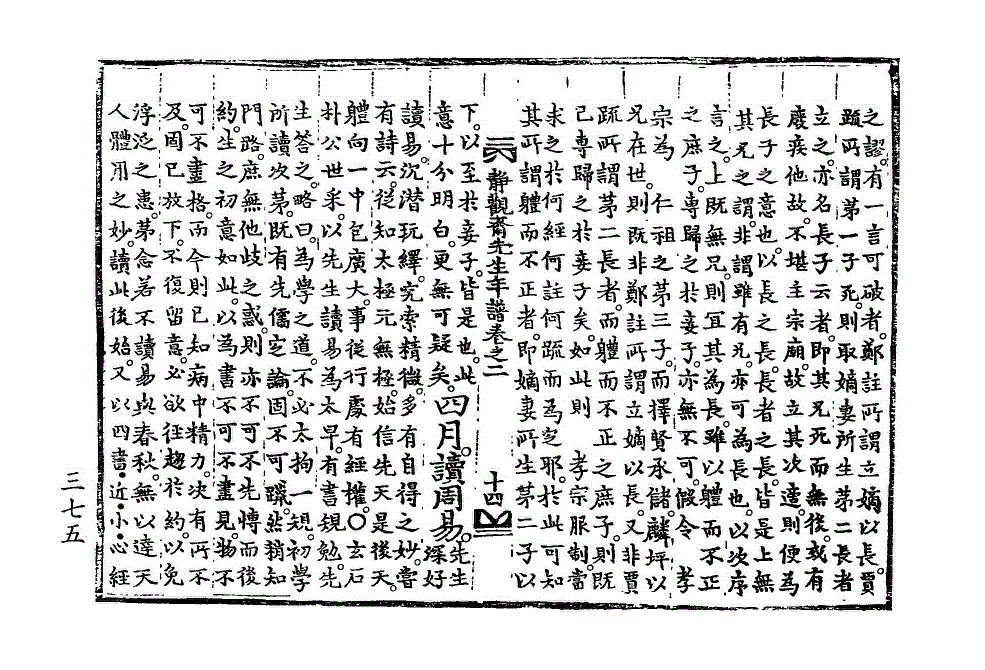 之谬。有一言可破者。郑注所谓立嫡以长。贾疏所谓第一子死。则取嫡妻所生第二长者立之。亦名长子云者。即其兄死而无后。或有废疾他故。不堪主宗庙。故立其次适。则便为长子之意也。以长之长。长者之长。皆是上无其兄之谓。非谓虽有兄。亦可为长也。以次序言之。上既无兄。则宜其为长。虽以体而不正之庶子。专归之于妾子。亦无不可。假令 孝宗为 仁祖之第三子。而择贤承储。麟坪以兄在世。则既非郑注所谓立嫡以长。又非贾疏所谓第二长者。而体而不正之庶子。则既已专归之于妾子矣。如此则 孝宗服制。当求之于何经何注何疏而为定耶。于此可知其所谓体而不正者。即嫡妻所生第二子以下。以至于妾子。皆是也。此意十分明白。更无可疑矣。)四月。读周易。(先生深好读易。沈潜玩绎。究索精微。多有自得之妙。尝有诗云。从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先天是后天。体向一中包广大。事从行处有经权。○玄石朴公世采。以先生读易为太早。有书规勉。先生答之。略曰。为学之道。不必太拘一规。初学所读次第。既有先儒定论。固不可躐。然稍知门路。庶无他岐之惑。则亦不可不先博而后约。生之初意如此。以为书不可不尽见。物不可不尽格。而今则已知病中精力。决有所不及。固已放下。不复留意。必欲径趋于约。以免浮泛之患。第念若不读易与春秋。无以达天人体用之妙。读此后始。又以四书,近,小,心经
之谬。有一言可破者。郑注所谓立嫡以长。贾疏所谓第一子死。则取嫡妻所生第二长者立之。亦名长子云者。即其兄死而无后。或有废疾他故。不堪主宗庙。故立其次适。则便为长子之意也。以长之长。长者之长。皆是上无其兄之谓。非谓虽有兄。亦可为长也。以次序言之。上既无兄。则宜其为长。虽以体而不正之庶子。专归之于妾子。亦无不可。假令 孝宗为 仁祖之第三子。而择贤承储。麟坪以兄在世。则既非郑注所谓立嫡以长。又非贾疏所谓第二长者。而体而不正之庶子。则既已专归之于妾子矣。如此则 孝宗服制。当求之于何经何注何疏而为定耶。于此可知其所谓体而不正者。即嫡妻所生第二子以下。以至于妾子。皆是也。此意十分明白。更无可疑矣。)四月。读周易。(先生深好读易。沈潜玩绎。究索精微。多有自得之妙。尝有诗云。从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先天是后天。体向一中包广大。事从行处有经权。○玄石朴公世采。以先生读易为太早。有书规勉。先生答之。略曰。为学之道。不必太拘一规。初学所读次第。既有先儒定论。固不可躐。然稍知门路。庶无他岐之惑。则亦不可不先博而后约。生之初意如此。以为书不可不尽见。物不可不尽格。而今则已知病中精力。决有所不及。固已放下。不复留意。必欲径趋于约。以免浮泛之患。第念若不读易与春秋。无以达天人体用之妙。读此后始。又以四书,近,小,心经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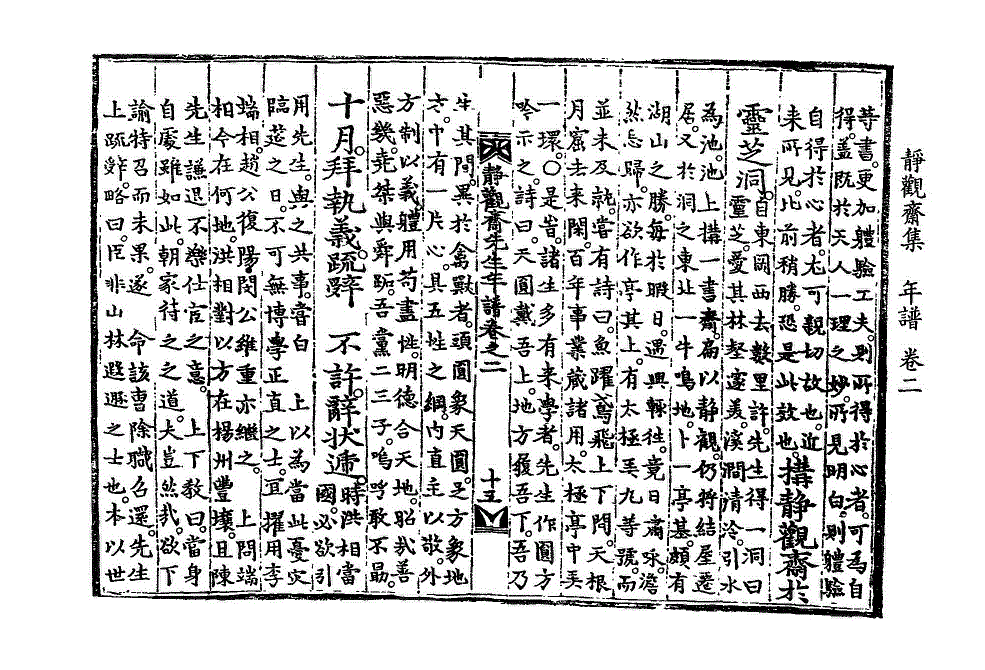 等书。更加体验工夫。则所得于心者。可为自得。盖既于天人一理之妙。所见明白。则体验自得于心者。尤可亲切故也。近来所见。比前稍胜。恐是此效也。)搆静观斋于灵芝洞。(自东冈西去数里许。先生得一洞曰灵芝。爱其林壑邃美。溪涧清泠。引水为池。池上搆一书斋。扁以静观。仍将结屋迁居。又于洞之东北一牛鸣地。卜一亭基。颇有湖山之胜。每于暇日。遇兴辄往。竟日肃咏。澹然忘归。亦欲作亭其上。有太极弄九等号。而并未及就。尝有诗曰。鱼跃鸢飞上下间。天根月窟去来闲。百年事业藏诸用。太极亭中弄一环。○是时。诸生多有来学者。先生作圆方吟示之。诗曰。天圆戴吾上。地方履吾下。吾乃生其间。异于禽兽者。头圆象天圆。足方象地方。中有一片心。具五性之纲。内直主以敬。外方制以义。体用苟尽性。明德合天地。昭哉善恶几。尧桀与舜蹠。吾党二三子。呜呼敢不勖。)十月。拜执义。疏辞 不许。辞状递。(时洪相当国。必欲引用先生。与之共事。尝白 上以为当此忧灾临筵之日。不可无博学正直之士。宜擢用李端相。赵公复阳,闵公维重亦继之。 上问端相今在何地。洪相对以方在杨州丰壤。且陈先生谦退不乐仕宦之意。 上下教曰。当身自处虽如此。朝家待之之道。夫岂然哉。欲下谕特召而未果。遂 命该曹除职召还。先生上疏辞。略曰。臣非山林遐遁之士也。本以世
等书。更加体验工夫。则所得于心者。可为自得。盖既于天人一理之妙。所见明白。则体验自得于心者。尤可亲切故也。近来所见。比前稍胜。恐是此效也。)搆静观斋于灵芝洞。(自东冈西去数里许。先生得一洞曰灵芝。爱其林壑邃美。溪涧清泠。引水为池。池上搆一书斋。扁以静观。仍将结屋迁居。又于洞之东北一牛鸣地。卜一亭基。颇有湖山之胜。每于暇日。遇兴辄往。竟日肃咏。澹然忘归。亦欲作亭其上。有太极弄九等号。而并未及就。尝有诗曰。鱼跃鸢飞上下间。天根月窟去来闲。百年事业藏诸用。太极亭中弄一环。○是时。诸生多有来学者。先生作圆方吟示之。诗曰。天圆戴吾上。地方履吾下。吾乃生其间。异于禽兽者。头圆象天圆。足方象地方。中有一片心。具五性之纲。内直主以敬。外方制以义。体用苟尽性。明德合天地。昭哉善恶几。尧桀与舜蹠。吾党二三子。呜呼敢不勖。)十月。拜执义。疏辞 不许。辞状递。(时洪相当国。必欲引用先生。与之共事。尝白 上以为当此忧灾临筵之日。不可无博学正直之士。宜擢用李端相。赵公复阳,闵公维重亦继之。 上问端相今在何地。洪相对以方在杨州丰壤。且陈先生谦退不乐仕宦之意。 上下教曰。当身自处虽如此。朝家待之之道。夫岂然哉。欲下谕特召而未果。遂 命该曹除职召还。先生上疏辞。略曰。臣非山林遐遁之士也。本以世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6L 页
 禄之臣。出入迩列。偏荷 洪造。而涓埃未报。遽婴奇疾。躬逢昭代。自为弃物。远隔 清光。退处空谷。甘忍穷饿。将与草木同腐。此岂臣之所欲哉。然臣伏闻 殿下于近者。连 御经筵。日讲心学。法天存诚。克尽修省之道。苟能终始不怠。无少间断。则将见上帝鬼神收还威怒。群黎百姓。无不蒙休。臣虽病死丘壑。与有荣矣。临疏涕泣。不知所云。)拜兼辅德。又辞得递。(时 春宫册礼迫近。降 旨促召。而先生又引疾呈状。盖先生退归已久。朝廷诸公。争劝一起。以承 上意。洪相则又有书曰。昔栗谷虽知牛溪多病。而以出入 经筵陈达。我虽不敢自比于昔贤。意则一也。又谓 春宫册礼时。则尤不可不起来。然先生益自撝谦。终始力辞而不进焉。)
禄之臣。出入迩列。偏荷 洪造。而涓埃未报。遽婴奇疾。躬逢昭代。自为弃物。远隔 清光。退处空谷。甘忍穷饿。将与草木同腐。此岂臣之所欲哉。然臣伏闻 殿下于近者。连 御经筵。日讲心学。法天存诚。克尽修省之道。苟能终始不怠。无少间断。则将见上帝鬼神收还威怒。群黎百姓。无不蒙休。臣虽病死丘壑。与有荣矣。临疏涕泣。不知所云。)拜兼辅德。又辞得递。(时 春宫册礼迫近。降 旨促召。而先生又引疾呈状。盖先生退归已久。朝廷诸公。争劝一起。以承 上意。洪相则又有书曰。昔栗谷虽知牛溪多病。而以出入 经筵陈达。我虽不敢自比于昔贤。意则一也。又谓 春宫册礼时。则尤不可不起来。然先生益自撝谦。终始力辞而不进焉。)四十年丁未。(先生四十岁)五月。拜辅德。屡辞 不许。以殿最居中递。(时右相郑公致和白 上曰。春宫辅导。此时正急。如李端相之儒雅博学。实合辅导。而以其恬退之故。该曹久不除职。宜有 召用之举矣。 上允之。遂有是除。)与松谷赵公(复阳)书。(时闽中人林寅观等。奉永历正朔。漂到耽罗。谓言 皇家一脉。尚在南隅。朝家将縳送虏中。先生闻之。不胜悲愤。尝屡与洪相往复。力言其不可。至是。又贻书赵公。略曰。我东于今日。纵不能观兵中国。一扫腥秽。以报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7H 页
 神宗皇帝之大德。其何忍反为此举。自丧秉彝之天哉。丙丁南汉椵锦之事。犹有可诿。此则虽有喙三寸。其将何以自解而更立于天壤间耶。若今庙议已定。牢不可破。则更无奈何。天运循环。行将有其时矣。此后君臣上下。果能惕然改图。誓不俱生。以继我 宁考之大志。少洒今日之耻。则庶有辞于天下后世矣。○翌年戊申春。又作序。寄耽罗牧使李公𡐔。其略曰。昔汉扬子云作太玄法言曰。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则是知新室不能亡汉。尚有后天之数。光武再造又二百馀年也。粤我 皇朝继宋而兴。创业之时。当后天一百二十世。 崇祯甲申 天王之祸。当后天一百二十八世。而再逢八八之灾者也。虽不敢明言显语。以漏天机。而运世年与直。卦与爻之应。亦可有推而知之者。考亭夫子于庆元己未。有诗曰。汉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岁又涒滩。仍自注曰。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息久之。盖宋室南迁后己未之岁。上距艺祖即阼之庚申。三周甲子。而韦斋发叹。其后甲子又一周。而考亭夫子有此诗。而宋室竟遂不振。此盖天地气数卦爻不协之验也。今者太岁在戊申。即我 太祖高皇帝即阼之年。而甲子已五周。恰是三百年矣。况其运世年之卦爻。适有与之相协者。安知甲申 天王之祸。不为汉之哀平之世合于中天之语。而尚有后天之数可以应光武中兴之期。不比于宋
神宗皇帝之大德。其何忍反为此举。自丧秉彝之天哉。丙丁南汉椵锦之事。犹有可诿。此则虽有喙三寸。其将何以自解而更立于天壤间耶。若今庙议已定。牢不可破。则更无奈何。天运循环。行将有其时矣。此后君臣上下。果能惕然改图。誓不俱生。以继我 宁考之大志。少洒今日之耻。则庶有辞于天下后世矣。○翌年戊申春。又作序。寄耽罗牧使李公𡐔。其略曰。昔汉扬子云作太玄法言曰。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则是知新室不能亡汉。尚有后天之数。光武再造又二百馀年也。粤我 皇朝继宋而兴。创业之时。当后天一百二十世。 崇祯甲申 天王之祸。当后天一百二十八世。而再逢八八之灾者也。虽不敢明言显语。以漏天机。而运世年与直。卦与爻之应。亦可有推而知之者。考亭夫子于庆元己未。有诗曰。汉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岁又涒滩。仍自注曰。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息久之。盖宋室南迁后己未之岁。上距艺祖即阼之庚申。三周甲子。而韦斋发叹。其后甲子又一周。而考亭夫子有此诗。而宋室竟遂不振。此盖天地气数卦爻不协之验也。今者太岁在戊申。即我 太祖高皇帝即阼之年。而甲子已五周。恰是三百年矣。况其运世年之卦爻。适有与之相协者。安知甲申 天王之祸。不为汉之哀平之世合于中天之语。而尚有后天之数可以应光武中兴之期。不比于宋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7L 页
 室之不振耶。闻耽罗有汉拿山者。其高可以俯临南极。李侯于暇日。试登其顶而望焉。则江南之某地某地。海外之某国某国。举在眼底。不待西湖之游。而亦可知春陵白水之佳气已浮于吴头楚尾之间矣。又安知不复有如林寅观者过而得遇李侯。更传天上消息耶。幸以此说。藏而秘之。默而待之也。)八月。往省外舅李孝贞公之墓。(墓在杨根。归路过石室。有诗曰。南极浮槎海上来。红云一朵日边开。千秋大义无人识。石室山前痛哭回。盖以才有林寅观事也。诗语激烈。慷慨一时。闻者争相传诵。尤斋亦和寄曰。飘然簪佩问何来。辽蓟腥云郁未开。吾人底事吞声哭。 先主陵前去复回。)九月。子极生。
室之不振耶。闻耽罗有汉拿山者。其高可以俯临南极。李侯于暇日。试登其顶而望焉。则江南之某地某地。海外之某国某国。举在眼底。不待西湖之游。而亦可知春陵白水之佳气已浮于吴头楚尾之间矣。又安知不复有如林寅观者过而得遇李侯。更传天上消息耶。幸以此说。藏而秘之。默而待之也。)八月。往省外舅李孝贞公之墓。(墓在杨根。归路过石室。有诗曰。南极浮槎海上来。红云一朵日边开。千秋大义无人识。石室山前痛哭回。盖以才有林寅观事也。诗语激烈。慷慨一时。闻者争相传诵。尤斋亦和寄曰。飘然簪佩问何来。辽蓟腥云郁未开。吾人底事吞声哭。 先主陵前去复回。)九月。子极生。四十一年戊申。(先生四十一岁。)二月。舟往骊江。会葬沂川洪相公。(先生与洪相契许甚至。不以年位有间。至是。洪相殁。先生哭之甚恸。有挽诗六百言。又操文具奠。扶病往会其葬。归时有诗曰。婆娑城外数重山。相国衣冠葬此间。江汉春风三百里。扁舟空载夕阳还。)三月。拜应教。一状三疏。并 不许。后以痘患辞。始递。(李公庆亿以大宪入侍。请 上勿许先生辞职。期令上来。并与在野儒臣。聚精会神。以为维持之地。故自 上靳许如此。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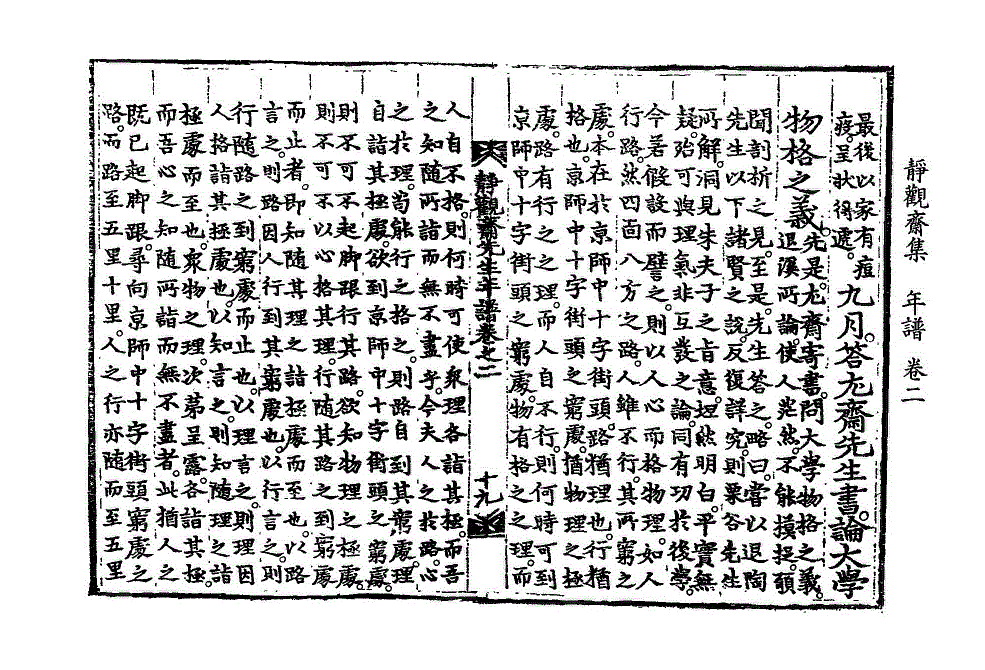 最后以家有痘疫。呈状得递。)九月。答尤斋先生书。论太学物格之义。(先是。尤斋寄书。问大学物格之义。退溪所论。使人茫然。不能摸捉。愿闻剖析之见。至是。先生答之。略曰。尝以退陶先生以下诸贤之说。反复详究。则栗谷先生所解。洞见朱夫子之旨意。坦然明白。平实无疑。殆可与理气非互发之论。同有功于后学。今若假设而譬之。则以人心而格物理。如人行路。然四面八方之路。人虽不行。其所穷之处。本在于京师中十字街头。路犹理也。行犹格也。京师中十字街头之穷处。犹物理之极处。路有行之之理。而人自不行。则何时可到京师中十字街头之穷处。物有格之之理。而人自不格。则何时可使众理各诣其极。而吾之知随所诣而无不尽乎。今夫人之于路。心之于理。苟能行之格之。则路自到其穷处。理自诣其极处。欲到京师中十字街头之穷处。则不可不起脚跟行其路。欲知物理之极处。则不可不以心格其理。行随其路之到穷处而止者。即知随其理之诣极处而至也。以路言之。则路因人行到其穷处也。以行言之。则行随路之到穷处而止也。以理言之。则理因人格诣其极处也。以知言之。则知随理之诣极处而至也。众物之理。次第呈露。各诣其极。而吾心之知随所诣而无不尽者。此犹人之既已起脚跟。寻向京师中十字街头穷处之路。而路至五里十里。人之行亦随而至五里
最后以家有痘疫。呈状得递。)九月。答尤斋先生书。论太学物格之义。(先是。尤斋寄书。问大学物格之义。退溪所论。使人茫然。不能摸捉。愿闻剖析之见。至是。先生答之。略曰。尝以退陶先生以下诸贤之说。反复详究。则栗谷先生所解。洞见朱夫子之旨意。坦然明白。平实无疑。殆可与理气非互发之论。同有功于后学。今若假设而譬之。则以人心而格物理。如人行路。然四面八方之路。人虽不行。其所穷之处。本在于京师中十字街头。路犹理也。行犹格也。京师中十字街头之穷处。犹物理之极处。路有行之之理。而人自不行。则何时可到京师中十字街头之穷处。物有格之之理。而人自不格。则何时可使众理各诣其极。而吾之知随所诣而无不尽乎。今夫人之于路。心之于理。苟能行之格之。则路自到其穷处。理自诣其极处。欲到京师中十字街头之穷处。则不可不起脚跟行其路。欲知物理之极处。则不可不以心格其理。行随其路之到穷处而止者。即知随其理之诣极处而至也。以路言之。则路因人行到其穷处也。以行言之。则行随路之到穷处而止也。以理言之。则理因人格诣其极处也。以知言之。则知随理之诣极处而至也。众物之理。次第呈露。各诣其极。而吾心之知随所诣而无不尽者。此犹人之既已起脚跟。寻向京师中十字街头穷处之路。而路至五里十里。人之行亦随而至五里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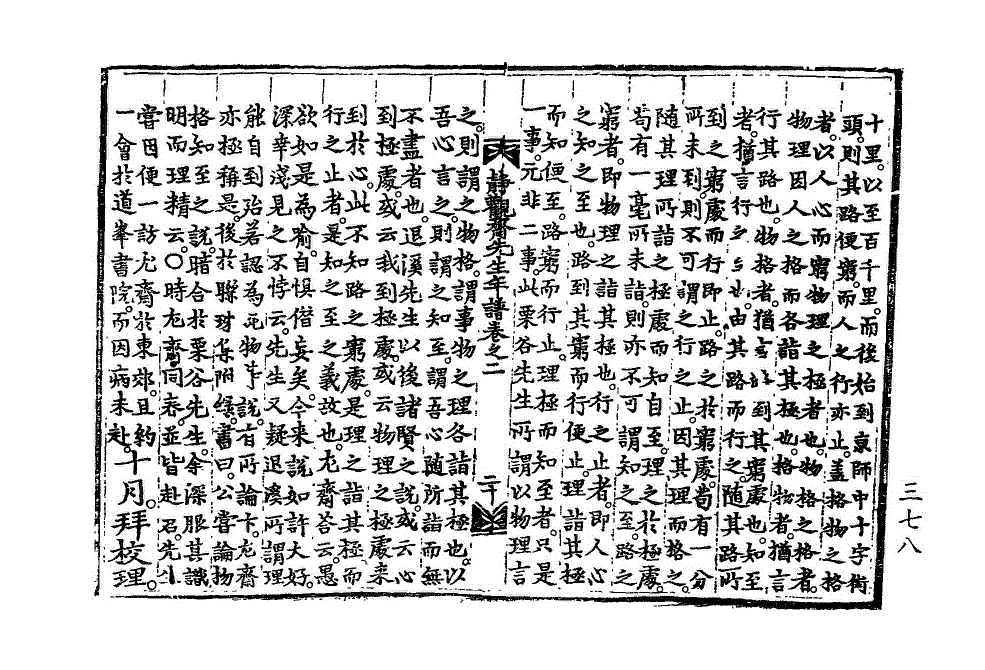 十里。以至百千里。而后始到京师中十字街头。则其路便穷。而人之行亦止。盖格物之格者。以人心而穷物理之极者也。物格之格者。物理因人之格而各诣其极也。格物者。犹言行其路也。物格者。犹言路到其穷处也。知至者。犹言行之至也。由其路而行之。随其路所到之穷处而行即止。路之于穷处。苟有一分所未到。则不可谓之行之止。因其理而格之。随其理所诣之极处而知自至。理之于极处。苟有一毫所未诣。则亦不可谓知之至。路之穷者。即物理之诣其极也。行之止者。即人心之知之至也。路到其穷而行便止。理诣其极而知便至。路穷而行止。理极而知至者。只是一事。元非二事。此栗谷先生所谓以物理言之。则谓之物格。谓事物之理各诣其极也。以吾心言之。则谓之知至。谓吾心随所诣而无不尽者也。退溪先生以后诸贤之说。或云心到极处。或云我到极处。或云物理之极处来到于心。此不知路之穷处。是理之诣其极。而行之止者。是知之至之义故也。尤斋答云。愚欲如是为喻。自惧僭妄矣。今来说如许大好。深幸浅见之不悖云。先生又疑退溪所谓理能自到殆若认为死物等说。有所论卞。尤斋亦极称是。后于联珠集附录。书曰。公尝论物格知至之说。暗合于栗谷先生。余深服其识明而理精云。○时尤斋,同春。并皆赴召。先生尝因便一访尤斋于东郊。且约一会于道峰书院。而因病未赴。)十月。拜校理。
十里。以至百千里。而后始到京师中十字街头。则其路便穷。而人之行亦止。盖格物之格者。以人心而穷物理之极者也。物格之格者。物理因人之格而各诣其极也。格物者。犹言行其路也。物格者。犹言路到其穷处也。知至者。犹言行之至也。由其路而行之。随其路所到之穷处而行即止。路之于穷处。苟有一分所未到。则不可谓之行之止。因其理而格之。随其理所诣之极处而知自至。理之于极处。苟有一毫所未诣。则亦不可谓知之至。路之穷者。即物理之诣其极也。行之止者。即人心之知之至也。路到其穷而行便止。理诣其极而知便至。路穷而行止。理极而知至者。只是一事。元非二事。此栗谷先生所谓以物理言之。则谓之物格。谓事物之理各诣其极也。以吾心言之。则谓之知至。谓吾心随所诣而无不尽者也。退溪先生以后诸贤之说。或云心到极处。或云我到极处。或云物理之极处来到于心。此不知路之穷处。是理之诣其极。而行之止者。是知之至之义故也。尤斋答云。愚欲如是为喻。自惧僭妄矣。今来说如许大好。深幸浅见之不悖云。先生又疑退溪所谓理能自到殆若认为死物等说。有所论卞。尤斋亦极称是。后于联珠集附录。书曰。公尝论物格知至之说。暗合于栗谷先生。余深服其识明而理精云。○时尤斋,同春。并皆赴召。先生尝因便一访尤斋于东郊。且约一会于道峰书院。而因病未赴。)十月。拜校理。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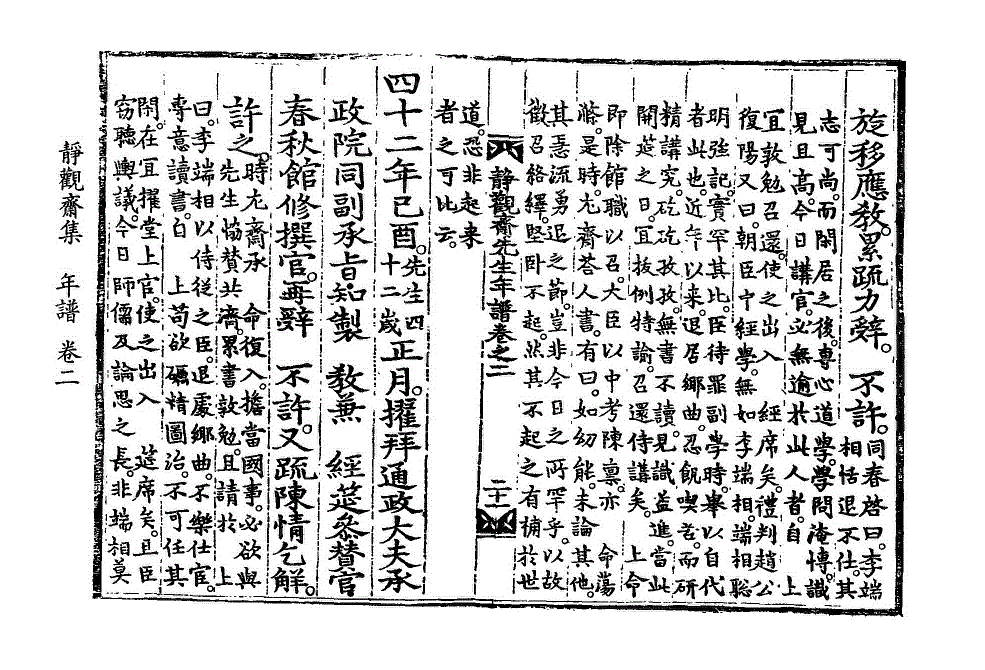 旋移应教。累疏力辞。 不许。(同春启曰。李端相恬退不仕。其志可尚。而闲居之后。专心道学。学问淹博。识见且高。今日讲官。必无逾于此人者。自 上宜敦勉召还。使之出入 经席矣。礼判赵公复阳又曰。朝臣中经学。无如李端相。端相聪明强记。实罕其比。臣待罪副学时。举以自代者此也。近年以来。退居乡曲。忍饥吃苦。而研精讲究。矻矻孜孜。无书不读。见识益进。当此开筵之日。宜拔例特谕。召还侍讲矣。 上命即除馆职以召。大臣以中考陈禀。亦 命荡涤。是时。尤斋答人书。有曰。如幼能。未论其他。其急流勇退之节。岂非今日之所罕乎。以故徵召络绎。坚卧不起。然其不起之有补于世道。恐非起来者之可比云。)
旋移应教。累疏力辞。 不许。(同春启曰。李端相恬退不仕。其志可尚。而闲居之后。专心道学。学问淹博。识见且高。今日讲官。必无逾于此人者。自 上宜敦勉召还。使之出入 经席矣。礼判赵公复阳又曰。朝臣中经学。无如李端相。端相聪明强记。实罕其比。臣待罪副学时。举以自代者此也。近年以来。退居乡曲。忍饥吃苦。而研精讲究。矻矻孜孜。无书不读。见识益进。当此开筵之日。宜拔例特谕。召还侍讲矣。 上命即除馆职以召。大臣以中考陈禀。亦 命荡涤。是时。尤斋答人书。有曰。如幼能。未论其他。其急流勇退之节。岂非今日之所罕乎。以故徵召络绎。坚卧不起。然其不起之有补于世道。恐非起来者之可比云。)四十二年己酉。(先生四十二岁)正月。擢拜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制 教兼 经筵参赞官,春秋馆修撰官。再辞 不许。又疏陈情乞解。许之。(时尤斋承 命复入。担当国事。必欲与先生协赞共济。累书敦勉。且请于 上曰。李端相以侍从之臣。退处乡曲。不乐仕宦。专意读书。白 上苟欲砺精图治。不可任其闲。在宜擢堂上官。使之出入 筵席矣。且臣窃听舆议。今日师儒及论思之长。非端相莫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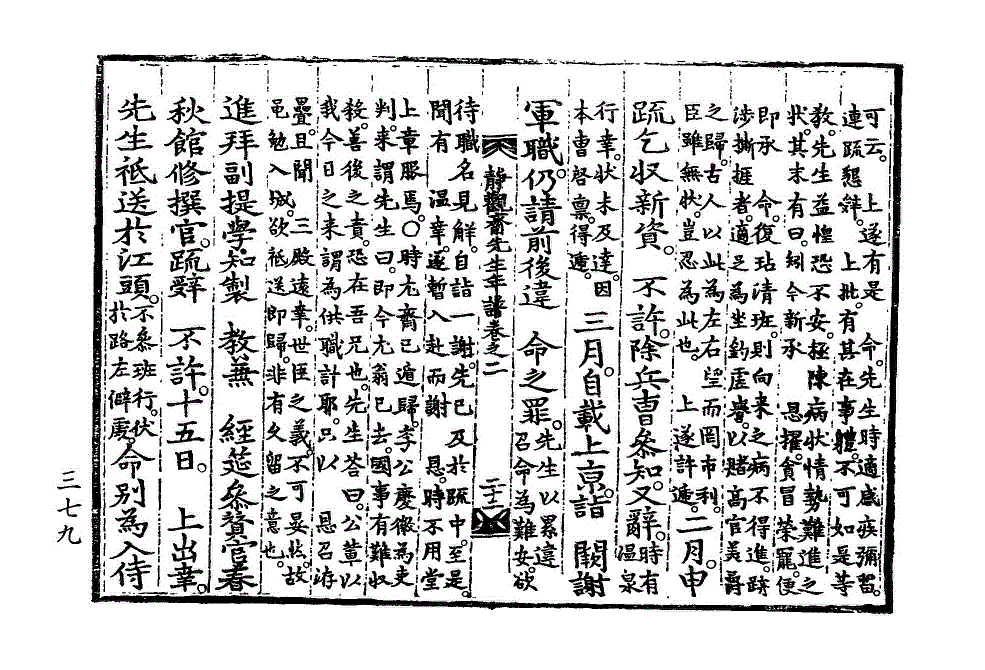 可云。 上遂有是 命。先生时适感疾弥留。连疏恳辞。 上批。有其在事体。不可如是等教。先生益惶恐不安。极陈病状情势难进之状。其末有曰。矧今新承 恩擢。贪冒荣宠。便即承 命。复玷清班。则向来之病不得进。迹涉撕挨者。适足为坐钓虚誉。以赌高官美爵之归。古人以此为左右望而罔市利。臣虽无状。岂忍为此也。 上遂许递。)二月。申疏乞收新资。 不许。除兵曹参知。又辞。(时有温泉行幸。状未及达。因本曹启禀。得递。)三月。自载上京。诣 阙谢军职。仍请前后违 命之罪。(先生以累违 召命为难安。欲待职名见解。自诣一谢。先已及于疏中。至是。闻有 温幸。遂暂入赴而谢 恩。时不用堂上章服焉。○时尤斋已遁归。李公庆徽为吏判。来谓先生曰。即今尤翁已去。国事有难收杀。善后之责。恐在吾兄也。先生答曰。公辈以我今日之来谓为供职计耶。只以 恩召荐叠。且闻 三殿远幸。世臣之义。不可晏然。故黾勉入城。欲祗送即归。非有久留之意也。)进拜副提学,知制 教兼 经筵参赞官,春秋馆修撰官。疏辞 不许。十五日。 上出幸。先生祗送于江头。(不参班行。伏于路左僻处。)命别为入侍
可云。 上遂有是 命。先生时适感疾弥留。连疏恳辞。 上批。有其在事体。不可如是等教。先生益惶恐不安。极陈病状情势难进之状。其末有曰。矧今新承 恩擢。贪冒荣宠。便即承 命。复玷清班。则向来之病不得进。迹涉撕挨者。适足为坐钓虚誉。以赌高官美爵之归。古人以此为左右望而罔市利。臣虽无状。岂忍为此也。 上遂许递。)二月。申疏乞收新资。 不许。除兵曹参知。又辞。(时有温泉行幸。状未及达。因本曹启禀。得递。)三月。自载上京。诣 阙谢军职。仍请前后违 命之罪。(先生以累违 召命为难安。欲待职名见解。自诣一谢。先已及于疏中。至是。闻有 温幸。遂暂入赴而谢 恩。时不用堂上章服焉。○时尤斋已遁归。李公庆徽为吏判。来谓先生曰。即今尤翁已去。国事有难收杀。善后之责。恐在吾兄也。先生答曰。公辈以我今日之来谓为供职计耶。只以 恩召荐叠。且闻 三殿远幸。世臣之义。不可晏然。故黾勉入城。欲祗送即归。非有久留之意也。)进拜副提学,知制 教兼 经筵参赞官,春秋馆修撰官。疏辞 不许。十五日。 上出幸。先生祗送于江头。(不参班行。伏于路左僻处。)命别为入侍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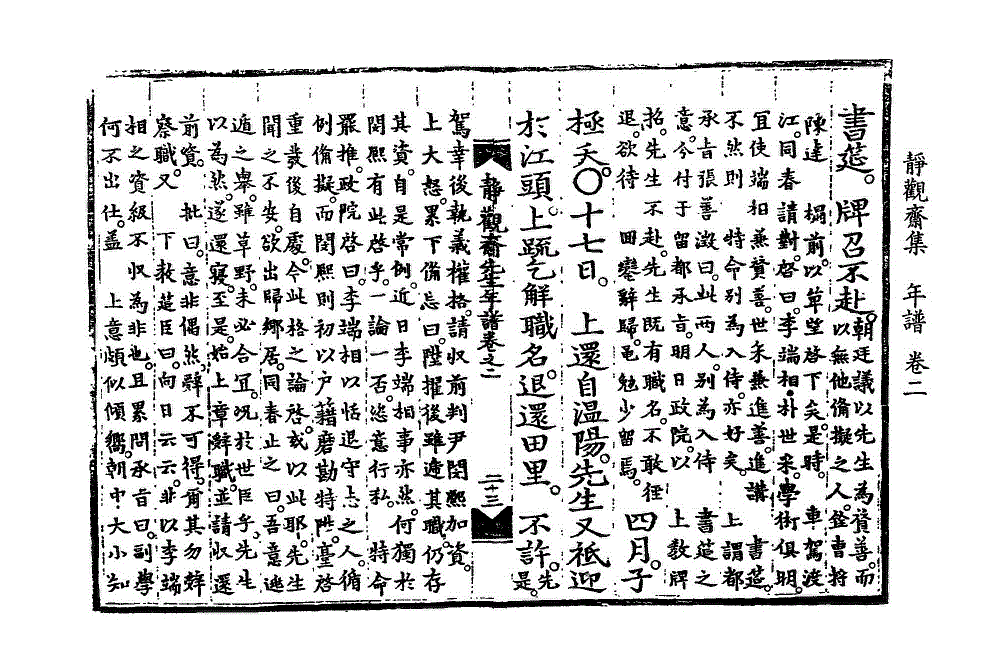 书筵。 牌召不赴。(朝廷议以先生为赞善。而以无他备拟之人。铨曹将陈达 榻前。以单望启下矣。是时。 车驾渡江。同春请对。启曰。李端相,朴世采。学术俱明。宜使端相兼赞善。世采兼进善。进讲 书筵。不然则 特命别为入侍。亦好矣。 上谓都承旨张善澄曰。此两人。别为入侍 书筵之意。分付于留都承旨。明日政院。以 上教牌招。先生不赴。先生既有职名。不敢径退。欲待 回銮辞归。黾勉少留焉。)四月。子极夭。○十七日。 上还自温阳。先生又祗迎于江头。上疏乞解职名。退还田里。 不许。(先是。驾幸后执义权格。请收前判尹闵熙加资。 上大怒。累下备忘曰。升擢后虽递其职。仍存其资。自是常例。近日李端相事亦然。何独于闵熙有此启乎。一论一否。恣意行私。 特命罢推。政院启曰。李端相以恬退守志之人。循例备拟。而闵熙则初以户籍磨勘特升。台启重发后自处。今此格之论启。或以此耶。先生闻之不安。欲出归乡居。同春止之曰。吾意逃遁之举。虽草野。未必合宜。况于世臣乎。先生以为然。遂还寝。至是。始上章辞职。并请收还前资。 批曰。意非偶然。辞不可得。尔其勿辞察职。又 下教筵臣曰。向日云云。非以李端相之资级不收为非也。且累问承旨曰。副学何不出仕。盖 上意颇似倾向。朝中大小知
书筵。 牌召不赴。(朝廷议以先生为赞善。而以无他备拟之人。铨曹将陈达 榻前。以单望启下矣。是时。 车驾渡江。同春请对。启曰。李端相,朴世采。学术俱明。宜使端相兼赞善。世采兼进善。进讲 书筵。不然则 特命别为入侍。亦好矣。 上谓都承旨张善澄曰。此两人。别为入侍 书筵之意。分付于留都承旨。明日政院。以 上教牌招。先生不赴。先生既有职名。不敢径退。欲待 回銮辞归。黾勉少留焉。)四月。子极夭。○十七日。 上还自温阳。先生又祗迎于江头。上疏乞解职名。退还田里。 不许。(先是。驾幸后执义权格。请收前判尹闵熙加资。 上大怒。累下备忘曰。升擢后虽递其职。仍存其资。自是常例。近日李端相事亦然。何独于闵熙有此启乎。一论一否。恣意行私。 特命罢推。政院启曰。李端相以恬退守志之人。循例备拟。而闵熙则初以户籍磨勘特升。台启重发后自处。今此格之论启。或以此耶。先生闻之不安。欲出归乡居。同春止之曰。吾意逃遁之举。虽草野。未必合宜。况于世臣乎。先生以为然。遂还寝。至是。始上章辞职。并请收还前资。 批曰。意非偶然。辞不可得。尔其勿辞察职。又 下教筵臣曰。向日云云。非以李端相之资级不收为非也。且累问承旨曰。副学何不出仕。盖 上意颇似倾向。朝中大小知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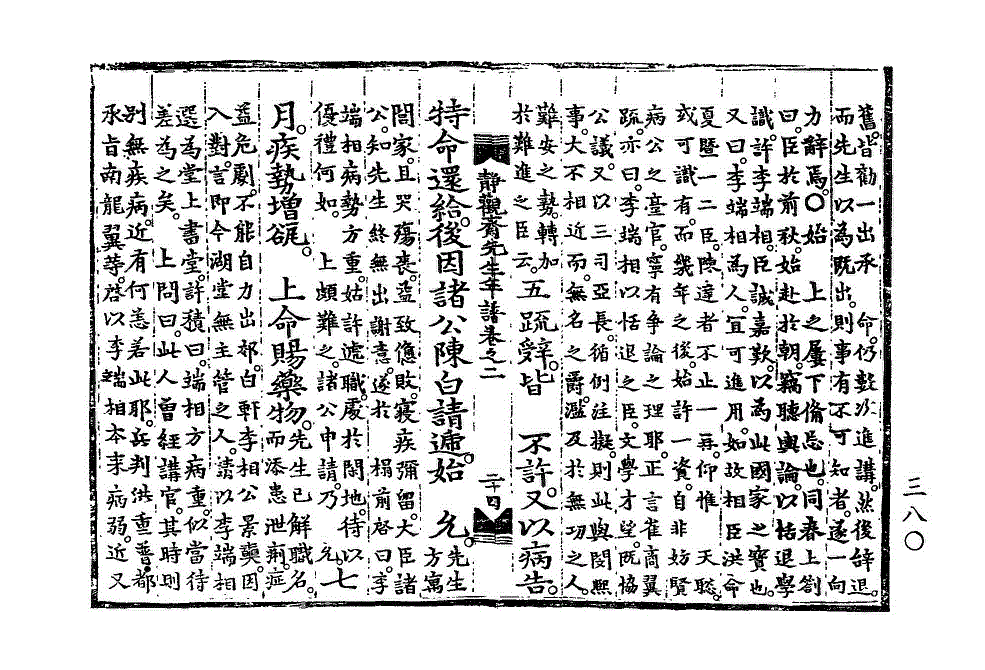 旧。皆劝一出承 命。仍数次进讲。然后辞退。而先生以为既出。则事有不可知者。遂一向力辞焉。○始 上之屡下备忘也。同春上劄曰。臣于前秋。始赴于朝。窃听舆论。以恬退学识。许李端相。臣诚嘉叹。以为此国家之宝也。又曰。李端相为人。宜可进用。如故相臣洪命夏暨一二臣。陈达者不止一再。仰惟 天聪。或可识有。而几年之后。始许一资。自非妨贤病公之台官。宁有争论之理耶。正言崔商翼疏。亦曰。李端相以恬退之臣。文学才望。既协公议。又以三司亚长。循例注拟。则此与闵熙事。大不相近而。无名之爵。滥及于无功之人。难安之势。转加于难进之臣云。)五疏辞。皆 不许。又以病告。特命还给。后因诸公陈白请递。始 允。(先生方寓闾家。且哭殇丧。益致惫败。寝疾弥留。大臣诸公。知先生终无出谢意。遂于 榻前启曰。李端相病势方重。姑许递职。处于闲地。待以优礼何如。 上颇难之。诸公申请。乃 允。)七月。疾势增谻。 上命赐药物。(先生已解职名。而添患泄痢。症益危剧。不能自力出郊。白轩李相公景奭。因入对。言即今湖堂无主管之人。请以李端相选为堂上书堂。许积曰。端相方病重。似当待差为之矣。 上问曰。此人曾经讲官。其时则别无疾病。近有何恙若此耶。兵判洪重普,都承旨南龙翼等。启以李端相本来病弱。近又
旧。皆劝一出承 命。仍数次进讲。然后辞退。而先生以为既出。则事有不可知者。遂一向力辞焉。○始 上之屡下备忘也。同春上劄曰。臣于前秋。始赴于朝。窃听舆论。以恬退学识。许李端相。臣诚嘉叹。以为此国家之宝也。又曰。李端相为人。宜可进用。如故相臣洪命夏暨一二臣。陈达者不止一再。仰惟 天聪。或可识有。而几年之后。始许一资。自非妨贤病公之台官。宁有争论之理耶。正言崔商翼疏。亦曰。李端相以恬退之臣。文学才望。既协公议。又以三司亚长。循例注拟。则此与闵熙事。大不相近而。无名之爵。滥及于无功之人。难安之势。转加于难进之臣云。)五疏辞。皆 不许。又以病告。特命还给。后因诸公陈白请递。始 允。(先生方寓闾家。且哭殇丧。益致惫败。寝疾弥留。大臣诸公。知先生终无出谢意。遂于 榻前启曰。李端相病势方重。姑许递职。处于闲地。待以优礼何如。 上颇难之。诸公申请。乃 允。)七月。疾势增谻。 上命赐药物。(先生已解职名。而添患泄痢。症益危剧。不能自力出郊。白轩李相公景奭。因入对。言即今湖堂无主管之人。请以李端相选为堂上书堂。许积曰。端相方病重。似当待差为之矣。 上问曰。此人曾经讲官。其时则别无疾病。近有何恙若此耶。兵判洪重普,都承旨南龙翼等。启以李端相本来病弱。近又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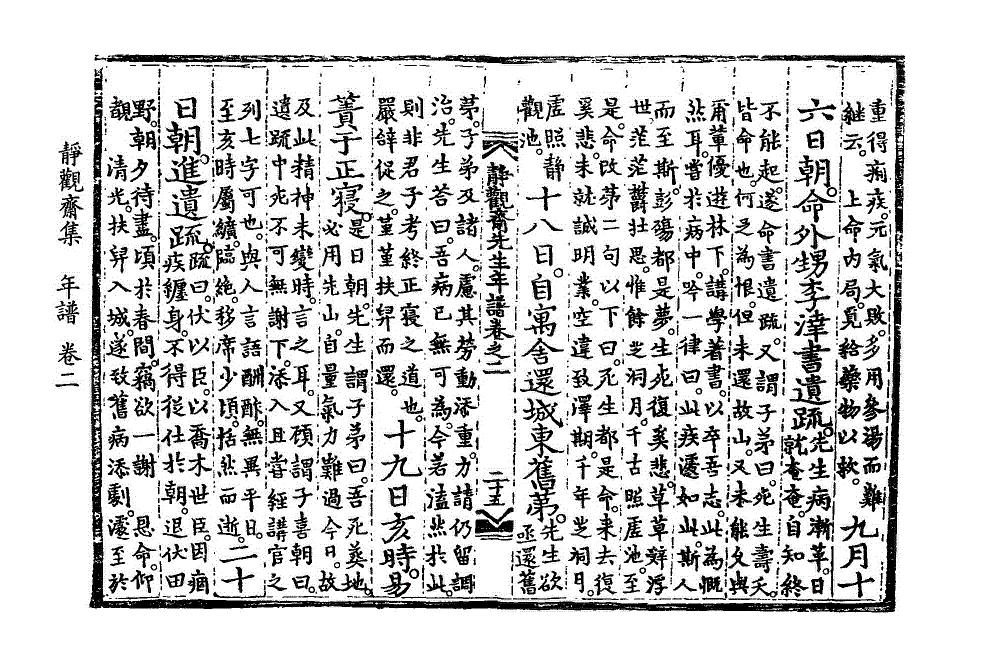 重得痢疾。元气大败。多用参汤而难继云。 上命内局。觅给药物以救。)九月十六日朝。命外甥李涬书遗疏。(先生病渐革。日就奄奄。自知终不能起。遂命书遗疏。又谓子弟曰。死生寿夭。皆命也。何足为恨。但未还故山。又未能久与尔辈优游林下。讲学著书。以卒吾志。此为慨然耳。尝于病中。吟一律曰。此疾遽如此。斯人而至斯。彭殇都是梦。生死复奚悲。草草辞浮世。茫茫郁壮思。惟馀芝洞月。千古照虚池。至是。命改第二句以下曰。死生都是命。来去复奚悲。未就诚明业。空违致泽期。千年芝洞月。虚照静观池。)十八日。自寓舍还城东旧第。(先生欲亟还旧第。子弟及诸人。虑其劳动添重。力诸仍留调治。先生答曰。吾病已无可为。今若溘然于此。则非君子考终正寝之道也。严辞促之。堇堇扶舁而还。)十九日亥时。易箦于正寝。(是日朝。先生谓子弟曰。吾死葬地。必用先山。自量气力难过今日。故及此精神未变时。言之耳。又顾谓子喜朝曰。遗疏中死不可无谢下。添入且尝经讲官之列七字可也。与人言语酬酢。无异平日。至亥时属纩。临绝。移席少顷。恬然而逝。)二十日朝。进遗疏。(疏曰。伏以臣。以乔木世臣。因痼疾缠身。不得从仕于朝。退伏田野。朝夕待尽。顷于春间。窃欲一谢 恩命。仰睹 清光。扶舁入城。遂致旧病添剧。遽至于
重得痢疾。元气大败。多用参汤而难继云。 上命内局。觅给药物以救。)九月十六日朝。命外甥李涬书遗疏。(先生病渐革。日就奄奄。自知终不能起。遂命书遗疏。又谓子弟曰。死生寿夭。皆命也。何足为恨。但未还故山。又未能久与尔辈优游林下。讲学著书。以卒吾志。此为慨然耳。尝于病中。吟一律曰。此疾遽如此。斯人而至斯。彭殇都是梦。生死复奚悲。草草辞浮世。茫茫郁壮思。惟馀芝洞月。千古照虚池。至是。命改第二句以下曰。死生都是命。来去复奚悲。未就诚明业。空违致泽期。千年芝洞月。虚照静观池。)十八日。自寓舍还城东旧第。(先生欲亟还旧第。子弟及诸人。虑其劳动添重。力诸仍留调治。先生答曰。吾病已无可为。今若溘然于此。则非君子考终正寝之道也。严辞促之。堇堇扶舁而还。)十九日亥时。易箦于正寝。(是日朝。先生谓子弟曰。吾死葬地。必用先山。自量气力难过今日。故及此精神未变时。言之耳。又顾谓子喜朝曰。遗疏中死不可无谢下。添入且尝经讲官之列七字可也。与人言语酬酢。无异平日。至亥时属纩。临绝。移席少顷。恬然而逝。)二十日朝。进遗疏。(疏曰。伏以臣。以乔木世臣。因痼疾缠身。不得从仕于朝。退伏田野。朝夕待尽。顷于春间。窃欲一谢 恩命。仰睹 清光。扶舁入城。遂致旧病添剧。遽至于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81L 页
 此。伏彖 圣慈矜怜。特赐内剂以救。其必欲其生之 盛意。天地难酬。而臣命迫运穷。终不起身。竟未得更瞻 龙颜而永辞 天日。臣虽入地。目不瞑矣。更有何言。更有何言。今此 贞陵祔庙之礼。实是千古之盛举。于此益可见 圣学之迥出百王。伏愿 圣明招延贤德。益懋大业。以光前烈。宋臣张栻之言曰。信任防一己之私。好恶公天下之理。斯言尽之矣。懋哉懋哉。臣官卑人贱。极知僭越。而君父赐药之恩。死不可无谢。且尝经讲官之列。谨裁短疏。兼陈区区之怀。临绝北望。稽首以进。○先生既殁。家无一衣。袭敛诸具。多用亲戚朋友所襚。士大夫倾朝来哭。远近士林闻者。莫不悲而惜之。○吏判赵公复阳启曰。故副提学李端相。身死之后。妻子贫穷。无以营葬。殊甚矜恻矣。 上命优赐米布。且给役夫。以庇葬事。○尤斋与人书曰。灵芝竟不起疾。吾道益孤矣。从此疑谁与质。病谁与砭。凉踽乎出门无适矣。又曰。幼能清名雅望。夙所倾向。而晚节所造。又非今世间可求者。又曰。幼能何处得来。今日知己绝矣。同春与人书。亦曰。斯人存没。似关时运。不敢私恸为也云。)十一月十九日。葬于加平朝宗县酉坐卯向之原。(在文靖公墓东北小冈外数十百步。)
此。伏彖 圣慈矜怜。特赐内剂以救。其必欲其生之 盛意。天地难酬。而臣命迫运穷。终不起身。竟未得更瞻 龙颜而永辞 天日。臣虽入地。目不瞑矣。更有何言。更有何言。今此 贞陵祔庙之礼。实是千古之盛举。于此益可见 圣学之迥出百王。伏愿 圣明招延贤德。益懋大业。以光前烈。宋臣张栻之言曰。信任防一己之私。好恶公天下之理。斯言尽之矣。懋哉懋哉。臣官卑人贱。极知僭越。而君父赐药之恩。死不可无谢。且尝经讲官之列。谨裁短疏。兼陈区区之怀。临绝北望。稽首以进。○先生既殁。家无一衣。袭敛诸具。多用亲戚朋友所襚。士大夫倾朝来哭。远近士林闻者。莫不悲而惜之。○吏判赵公复阳启曰。故副提学李端相。身死之后。妻子贫穷。无以营葬。殊甚矜恻矣。 上命优赐米布。且给役夫。以庇葬事。○尤斋与人书曰。灵芝竟不起疾。吾道益孤矣。从此疑谁与质。病谁与砭。凉踽乎出门无适矣。又曰。幼能清名雅望。夙所倾向。而晚节所造。又非今世间可求者。又曰。幼能何处得来。今日知己绝矣。同春与人书。亦曰。斯人存没。似关时运。不敢私恸为也云。)十一月十九日。葬于加平朝宗县酉坐卯向之原。(在文靖公墓东北小冈外数十百步。)四十五年壬子。行状成。(子喜朝撰次年谱。就正于文谷。因请状于玄石。)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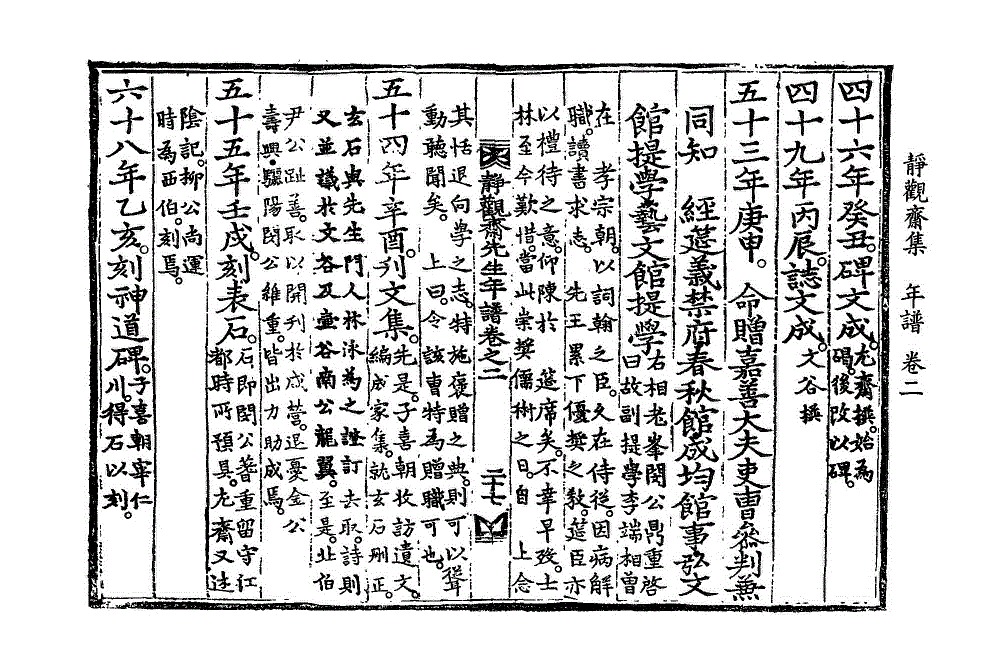 四十六年癸丑。碑文成。(尤斋撰。始为碣。后改以碑。)
四十六年癸丑。碑文成。(尤斋撰。始为碣。后改以碑。)四十九年丙辰。志文成。(文谷撰)
五十三年庚申。 命赠嘉善大夫吏曹参判兼同知 经筵义禁府,春秋馆,成均馆事,弘文馆提学,艺文馆提学(右相老峰闵公鼎重启曰故副提学李端相曾在 孝宗朝。以词翰之臣。久在侍从。因病解职。读书求志。 先王累下优奖之教。筵臣亦以礼待之意。仰陈于 筵席矣。不幸早殁。士林至今叹惜。当此崇奖儒术之日。自 上念其恬退向学之志。特施褒赠之典。则可以耸动听闻矣。 上曰。令该曹特为赠职可也。)
五十四年辛酉。刊文集。(先是。子喜朝收访遗文。编成家集。就玄石删正。玄石与先生门人林泳为之證订去取。诗则又并议于文谷及壶谷南公龙翼。至是。北伯尹公趾善。取以开刊于咸营。退忧金公寿兴,骊阳闵公维重。皆出力助成焉。)
五十五年壬戌。刻表石。(石即闵公蓍重留守江都时所预具。尤斋又述阴记。柳公尚运时为西伯。刻焉。)
六十八年乙亥。刻神道碑。(子喜朝宰仁川。得石以刻。)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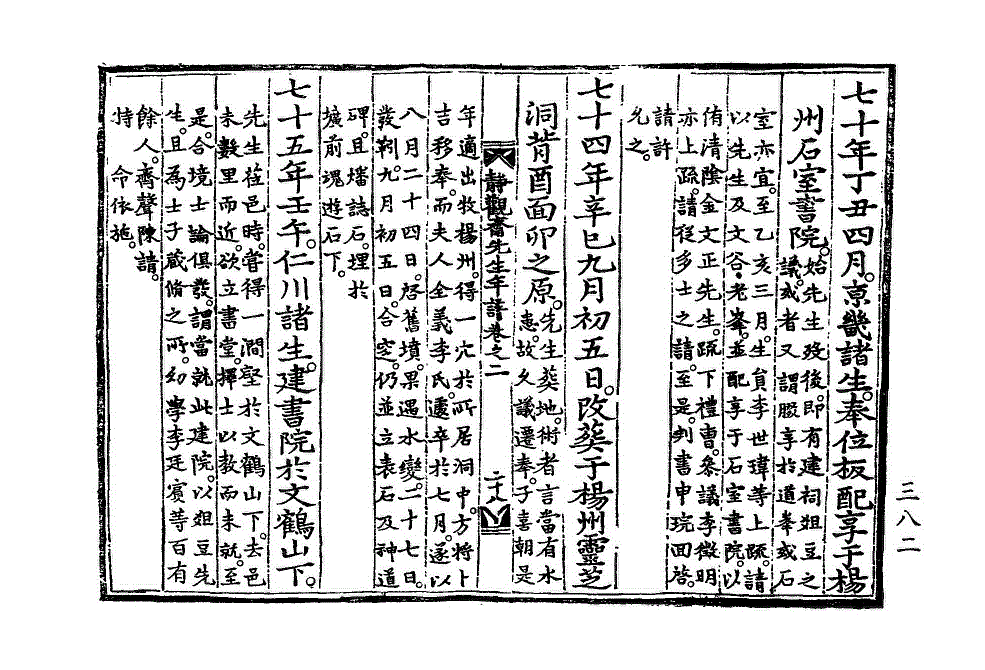 七十年丁丑四月。京畿诸生。奉位板配享于杨州石室书院。(始先生殁后。即有建祠俎豆之议。或者又谓啜享于道峰或石室亦宜。至乙亥三月。生员李世玮等上疏。请以先生及文谷,老峰。并配享于石室书院。以侑清阴金文正先生。疏下礼曹。参议李徵明亦上疏。请从多士之请。至是。判书申琓回启。请许允之。)
七十年丁丑四月。京畿诸生。奉位板配享于杨州石室书院。(始先生殁后。即有建祠俎豆之议。或者又谓啜享于道峰或石室亦宜。至乙亥三月。生员李世玮等上疏。请以先生及文谷,老峰。并配享于石室书院。以侑清阴金文正先生。疏下礼曹。参议李徵明亦上疏。请从多士之请。至是。判书申琓回启。请许允之。)七十四年辛巳九月初五日。改葬于杨州灵芝洞背酉面卯之原。(先生葬地。术者言当有水患。故久议迁奉。子喜朝是年适出牧杨州。得一穴于所居洞中。方将卜吉移奉。而夫人全义李氏。遽卒于七月。遂以八月二十四日。启旧坟。果遇水变。二十七日。发靷。九月初五日。合窆。仍并立表石及神道碑。且燔志石。埋于圹前魂游石下。)
七十五年壬午。仁川诸生。建书院于文鹤山下。(先生莅邑时。尝得一涧壑于文鹤山下。去邑未数里而近。欲立书堂。择士以教而未就。至是。合境士论俱发。谓当就此建院。以俎豆先生。且为士子藏脩之所。幼学李廷宾等百有馀人。齐声陈请。特 命依施。)
静观斋先生集年谱卷之二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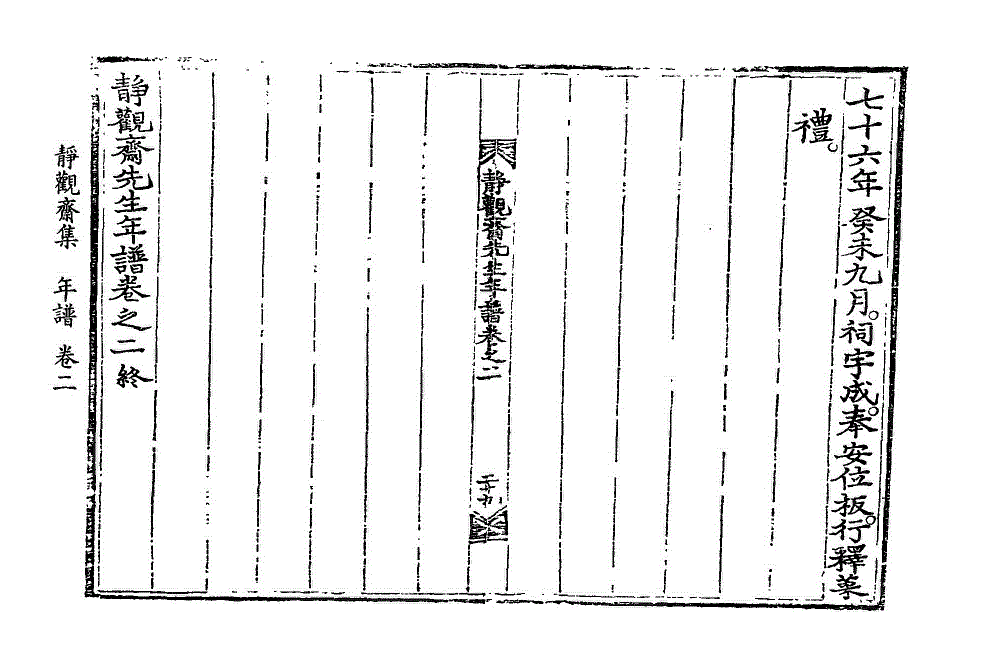 七十六年癸未九月。祠宇成。奉安位板。行释菜礼。
七十六年癸未九月。祠宇成。奉安位板。行释菜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