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x 页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书
书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47H 页
 答崔伯谦(道鸣)人心道心说因禀质函丈(己丑○伯谦襄阳人。关东大儒也。以其所为理气四七辨一篇。禀达于函丈。欲得折衷之诲。函丈递与得中。使之辨说以答之。故谨草呈于函丈。因以为讲质之地。)
答崔伯谦(道鸣)人心道心说因禀质函丈(己丑○伯谦襄阳人。关东大儒也。以其所为理气四七辨一篇。禀达于函丈。欲得折衷之诲。函丈递与得中。使之辨说以答之。故谨草呈于函丈。因以为讲质之地。)所论大槩得之。然于语意之间。或有未稳。玆敢依下教之意。略有辨说如左。
以道心为不掩于形气。人心为掩于形气一段。似未安。道心之发。直原性命。不犯形气。初不可以不掩言也。既发之后。有不能直遂其正者。是为形气所掩也。人心之发。自是生于形气。掩之一字。著不可得。道心无以宰之。则反有掩于道心耳。
夫既有耳目口鼻四肢之体。则不得不有欲声欲色欲味欲臭欲安逸之心。所谓上知之不能无者也。但既是我之所独。故无以宰之。则每向私一边引将去。以有无限不好事。而道心之不能直遂其情者。亦由于为其所掩也。此人心之所以为危。而道心之微亦以此也。若曰道心之发。不为形气所掩。则可以直遂其性命之正。一为形气所掩。则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正。人心之发。听命于道心。则为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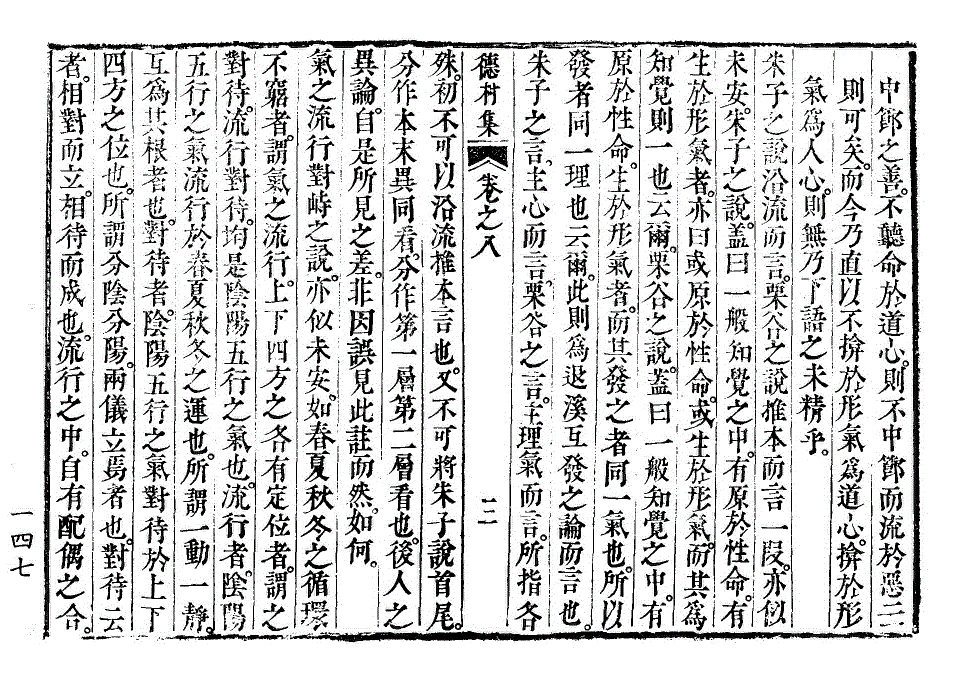 中节之善。不听命于道心。则不中节而流于恶云则可矣。而今乃直以不掩于形气为道心。掩于形气为人心。则无乃下语之未精乎。
中节之善。不听命于道心。则不中节而流于恶云则可矣。而今乃直以不掩于形气为道心。掩于形气为人心。则无乃下语之未精乎。朱子之说沿流而言。栗谷之说推本而言一段。亦似未安。朱子之说。盖曰一般知觉之中。有原于性命。有生于形气者。亦曰或原于性命。或生于形气。而其为知觉则一也云尔。栗谷之说。盖曰一般知觉之中。有原于性命。生于形气者。而其发之者同一气也。所以发者同一理也云尔。此则为退溪互发之论而言也。朱子之言。主心而言。栗谷之言。主理气而言。所指各殊。初不可以沿流推本言也。又不可将朱子说首尾。分作本末异同看。分作第一层第二层看也。后人之异论。自是所见之差。非因误见此注而然。如何。
气之流行对峙之说。亦似未安。如春夏秋冬之循环不穷者。谓气之流行。上下四方之各有定位者。谓之对待。流行对待。均是阴阳五行之气也。流行者。阴阳五行之气流行于春夏秋冬之运也。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也。对待者。阴阳五行之气对待于上下四方之位也。所谓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对待云者。相对而立。相待而成也。流行之中。自有配偶之合。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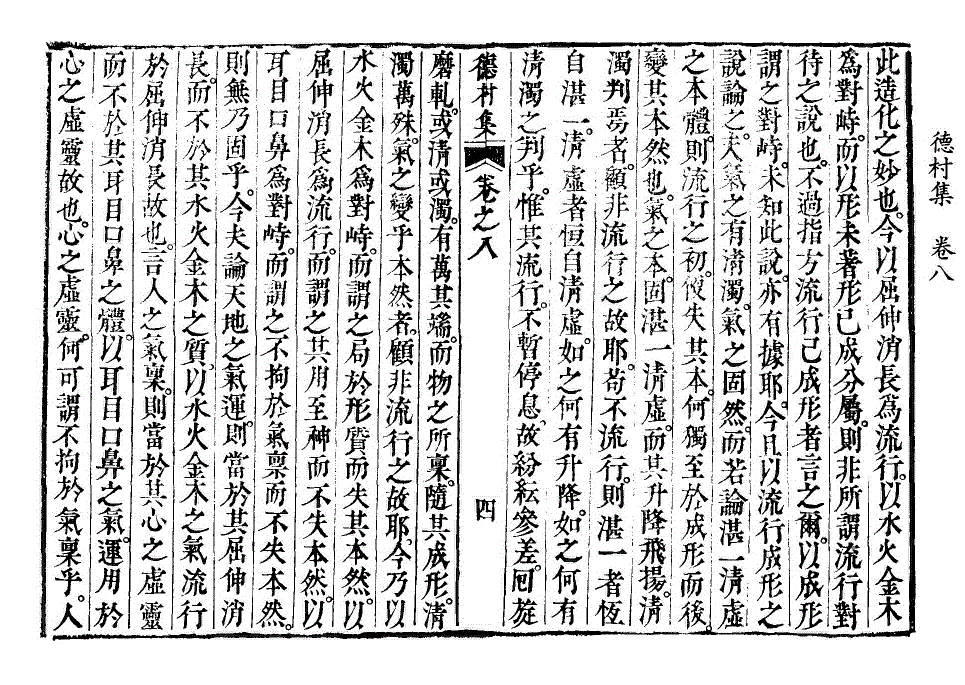 此造化之妙也。今以屈伸消长为流行。以水火金木为对峙。而以形未著形已成分属。则非所谓流行对待之说也。不过指方流行已成形者言之尔。以成形谓之对峙。未知此说。亦有据耶。今且以流行成形之说论之。夫气之有清浊。气之固然。而若论湛一清虚之本体。则流行之初。便失其本。何独至于成形而后。变其本然也。气之本。固湛一清虚。而其升降飞扬。清浊判焉者。顾非流行之故耶。苟不流行。则湛一者恒自湛一。清虚者恒自清虚。如之何有升降。如之何有清浊之判乎。惟其流行。不暂停息。故纷纭参差。回旋磨轧。或清或浊。有万其端。而物之所禀。随其成形。清浊万殊。气之变乎本然者。顾非流行之故耶。今乃以水火金木为对峙。而谓之局于形质而失其本然。以屈伸消长为流行。而谓之其用至神而不失本然。以耳目口鼻为对峙。而谓之不拘于气禀而不失本然。则无乃固乎。今夫论天地之气运。则当于其屈伸消长。而不于其水火金木之质。以水火金木之气流行于屈伸消长故也。言人之气禀。则当于其心之虚灵而不于其耳目口鼻之体。以耳目口鼻之气。运用于心之虚灵故也。心之虚灵。何可谓不拘于气禀乎。人
此造化之妙也。今以屈伸消长为流行。以水火金木为对峙。而以形未著形已成分属。则非所谓流行对待之说也。不过指方流行已成形者言之尔。以成形谓之对峙。未知此说。亦有据耶。今且以流行成形之说论之。夫气之有清浊。气之固然。而若论湛一清虚之本体。则流行之初。便失其本。何独至于成形而后。变其本然也。气之本。固湛一清虚。而其升降飞扬。清浊判焉者。顾非流行之故耶。苟不流行。则湛一者恒自湛一。清虚者恒自清虚。如之何有升降。如之何有清浊之判乎。惟其流行。不暂停息。故纷纭参差。回旋磨轧。或清或浊。有万其端。而物之所禀。随其成形。清浊万殊。气之变乎本然者。顾非流行之故耶。今乃以水火金木为对峙。而谓之局于形质而失其本然。以屈伸消长为流行。而谓之其用至神而不失本然。以耳目口鼻为对峙。而谓之不拘于气禀而不失本然。则无乃固乎。今夫论天地之气运。则当于其屈伸消长。而不于其水火金木之质。以水火金木之气流行于屈伸消长故也。言人之气禀。则当于其心之虚灵而不于其耳目口鼻之体。以耳目口鼻之气。运用于心之虚灵故也。心之虚灵。何可谓不拘于气禀乎。人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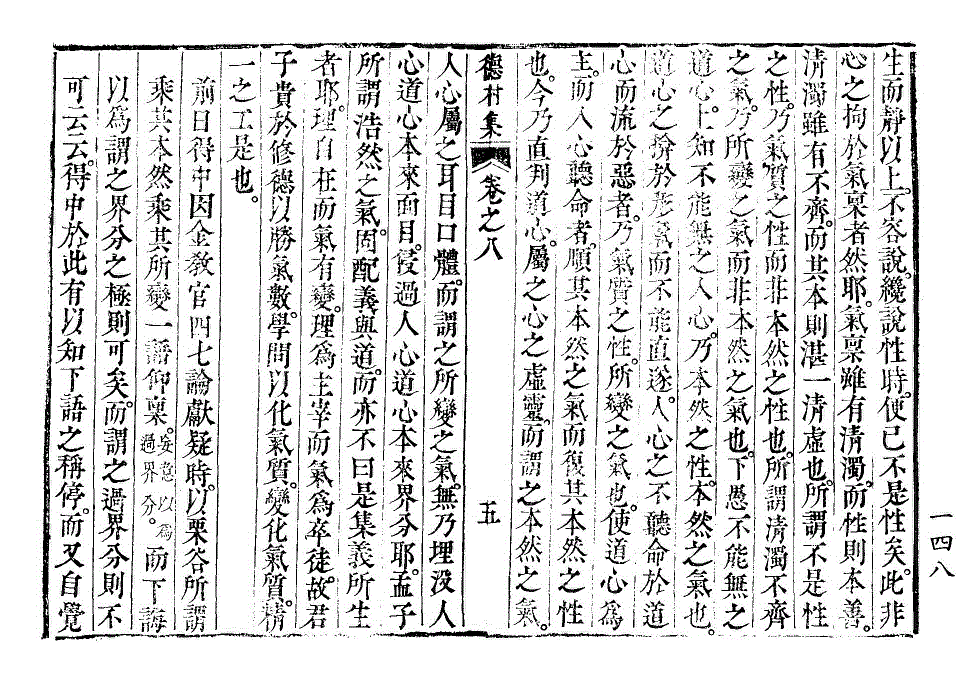 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矣。此非心之拘于气禀者然耶。气禀虽有清浊。而性则本善。清浊虽有不齐。而其本则湛一清虚也。所谓不是性之性。乃气质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也。所谓清浊不齐之气。乃所变之气而非本然之气也。下愚不能无之道心。上知不能无之人心。乃本然之性。本然之气也。道心之掩于形气而不能直遂。人心之不听命于道心而流于恶者。乃气质之性。所变之气也。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者。顺其本然之气而复其本然之性也。今乃直判道心。属之心之虚灵。而谓之本然之气。人心属之耳目口体。而谓之所变之气。无乃埋没人心道心本来面目。侵过人心道心本来界分耶。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固配义与道。而亦不曰是集义所生者耶。理自在而气有变。理为主宰而气为卒徒。故君子贵于修德以胜气数。学问以化气质。变化气质。精一之工是也。
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矣。此非心之拘于气禀者然耶。气禀虽有清浊。而性则本善。清浊虽有不齐。而其本则湛一清虚也。所谓不是性之性。乃气质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也。所谓清浊不齐之气。乃所变之气而非本然之气也。下愚不能无之道心。上知不能无之人心。乃本然之性。本然之气也。道心之掩于形气而不能直遂。人心之不听命于道心而流于恶者。乃气质之性。所变之气也。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者。顺其本然之气而复其本然之性也。今乃直判道心。属之心之虚灵。而谓之本然之气。人心属之耳目口体。而谓之所变之气。无乃埋没人心道心本来面目。侵过人心道心本来界分耶。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固配义与道。而亦不曰是集义所生者耶。理自在而气有变。理为主宰而气为卒徒。故君子贵于修德以胜气数。学问以化气质。变化气质。精一之工是也。前日得中因金教官四七论献疑时。以栗谷所谓乘其本然乘其所变一语仰禀。(妄意以为过界分。)而下诲以为谓之界分之极则可矣。而谓之过界分则不可云云。得中于此有以知下语之称停。而又自觉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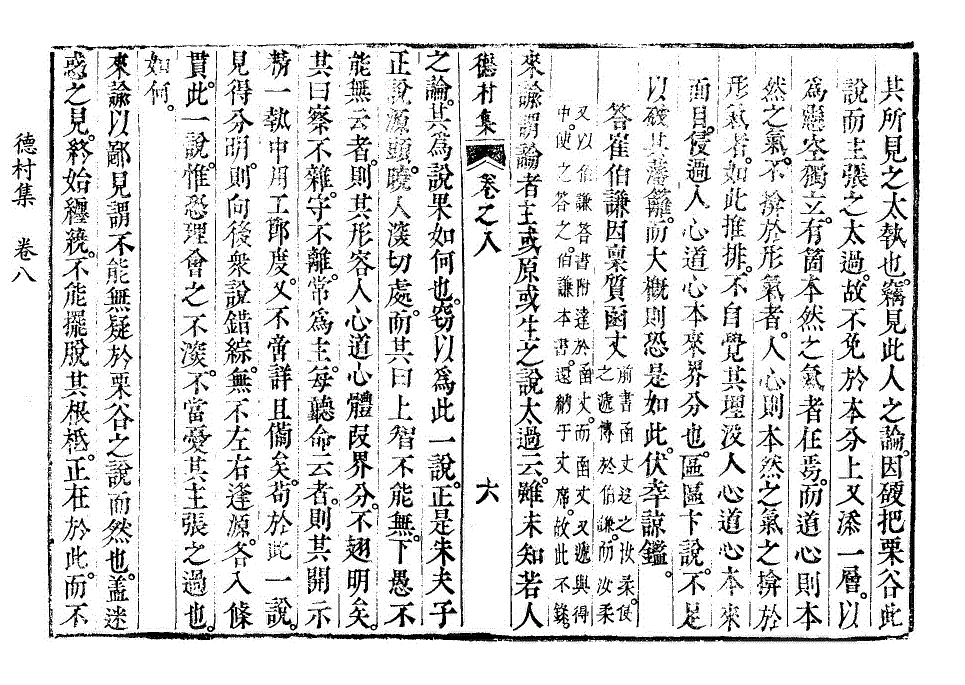 其所见之太执也。窃见此人之论。因硬把栗谷此说而主张之太过。故不免于本分上又添一层。以为悬空独立。有个本然之气者在焉。而道心则本然之气。不掩于形气者。人心则本然之气之掩于形气者。如此推排。不自觉其埋没人心道心本来面目。侵过人心道心本来界分也。区区卞说。不足以破其藩篱。而大概则恐是如此。伏幸谅鉴。
其所见之太执也。窃见此人之论。因硬把栗谷此说而主张之太过。故不免于本分上又添一层。以为悬空独立。有个本然之气者在焉。而道心则本然之气。不掩于形气者。人心则本然之气之掩于形气者。如此推排。不自觉其埋没人心道心本来面目。侵过人心道心本来界分也。区区卞说。不足以破其藩篱。而大概则恐是如此。伏幸谅鉴。答崔伯谦因禀质函丈(前书函丈送之汝柔。使之递传于伯谦。而汝柔又以伯谦答书附达于函丈。而函丈又递与得中。使之答之。伯谦本书。还纳于丈席。故此不录。)
来谕谓论者主或原或生之说太过云。虽未知若人之论。其为说果如何也。窃以为此一说。正是朱夫子正说源头。晓人深切处。而其曰上智不能无。下愚不能无云者。则其形容人心道心体段界分。不翅明矣。其曰察不杂。守不离。常为主。每听命云者。则其开示精一执中用工节度。又不啻详且备矣。苟于此一说。见得分明。则向后众说错综。无不左右逢源。各入条贯。此一说。惟恐理会之不深。不当忧其主张之过也。如何。
来谕以鄙见谓不能无疑于栗谷之说而然也。盖迷惑之见。终始缠绕。不能摆脱其根柢。正在于此。而不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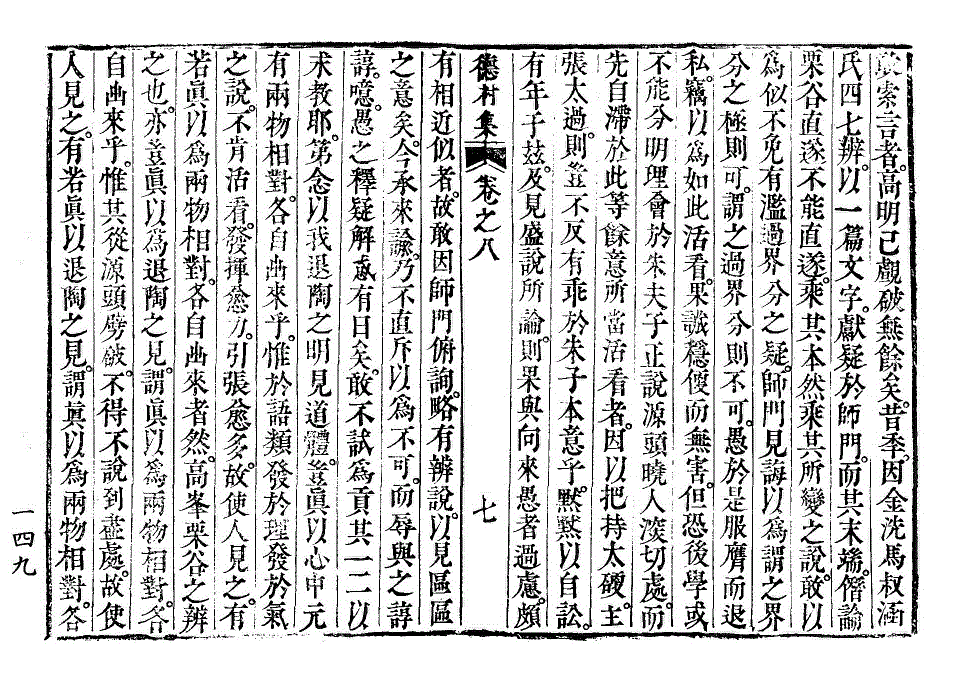 敢索言者。高明已觑破无馀矣。昔年。因金洗马叔涵氏四七辨。以一篇文字。献疑于师门。而其末端。僭论栗谷直遂不能直遂。乘其本然乘其所变之说。敢以为似不免有滥过界分之疑。师门见诲以为谓之界分之极则可。谓之过界分则不可。愚于是服膺而退私。窃以为如此活看。果诚稳便而无害。但恐后学或不能分明理会于朱夫子正说源头晓人深切处。而先自滞于此等馀意所当活看者。因以把持太硬。主张太过。则岂不反有乖于朱子本意乎。默默以自讼。有年于玆。及见盛说所论。则果与向来愚者过虑。颇有相近似者。故敢因师门俯询。略有辨说。以见区区之意矣。今承来谕。乃不直斥以为不可。而辱与之谆谆。噫。愚之释疑解惑有日矣。敢不试为贡其一二以求教耶。第念以我退陶之明见道体。岂真以心中元有两物相对。各自出来乎。惟于语类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不肯活看。发挥愈力。引张愈多。故使人见之。有若真以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者然。高峰栗谷之辨之也。亦岂真以为退陶之见。谓真以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乎。惟其从源头劈破。不得不说到尽处。故使人见之。有若真以退陶之见。谓真以为两物相对。各
敢索言者。高明已觑破无馀矣。昔年。因金洗马叔涵氏四七辨。以一篇文字。献疑于师门。而其末端。僭论栗谷直遂不能直遂。乘其本然乘其所变之说。敢以为似不免有滥过界分之疑。师门见诲以为谓之界分之极则可。谓之过界分则不可。愚于是服膺而退私。窃以为如此活看。果诚稳便而无害。但恐后学或不能分明理会于朱夫子正说源头晓人深切处。而先自滞于此等馀意所当活看者。因以把持太硬。主张太过。则岂不反有乖于朱子本意乎。默默以自讼。有年于玆。及见盛说所论。则果与向来愚者过虑。颇有相近似者。故敢因师门俯询。略有辨说。以见区区之意矣。今承来谕。乃不直斥以为不可。而辱与之谆谆。噫。愚之释疑解惑有日矣。敢不试为贡其一二以求教耶。第念以我退陶之明见道体。岂真以心中元有两物相对。各自出来乎。惟于语类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不肯活看。发挥愈力。引张愈多。故使人见之。有若真以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者然。高峰栗谷之辨之也。亦岂真以为退陶之见。谓真以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乎。惟其从源头劈破。不得不说到尽处。故使人见之。有若真以退陶之见。谓真以为两物相对。各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0H 页
 自出来者然。今日高明之力主乘其本然乘其所变之说。如此伸长。无亦近于退陶之力主发于理发于气之说而反不免有累于元来正知见乎。
自出来者然。今日高明之力主乘其本然乘其所变之说。如此伸长。无亦近于退陶之力主发于理发于气之说而反不免有累于元来正知见乎。语类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不过原于生于之意而已。退陶不肯活看。以有互发随乘内出外感之说。则其分开亦甚矣。栗谷之辨之诚是矣。而从今观之。又似不能无憾焉。今请先论退溪之说。而因及其所以不能无疑于栗谷之说之意也。盖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云者。主理气而言。理气妙用。元来如此也。原于性命生于形气云者。主心而言情之发。有此二途也。情之发。有此二途。而其为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则同也。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则同。而不害其为情之发。有此二途也。同是一气。同是一理。而其所主而言。则不容无别。发之所以发之云。主理气而言也。原于生于之云。主心而言也。从其所主而观。则二说同异。各极其趣。而不相妨夺矣。主心而观。则人心道心固有性命形气之分。而其同为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固自在矣。主理气而观。则人心道心。同是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而其各有性命形气之分。亦自在矣。斯岂非二说各极其趣而不相妨夺乎。发于理发于气之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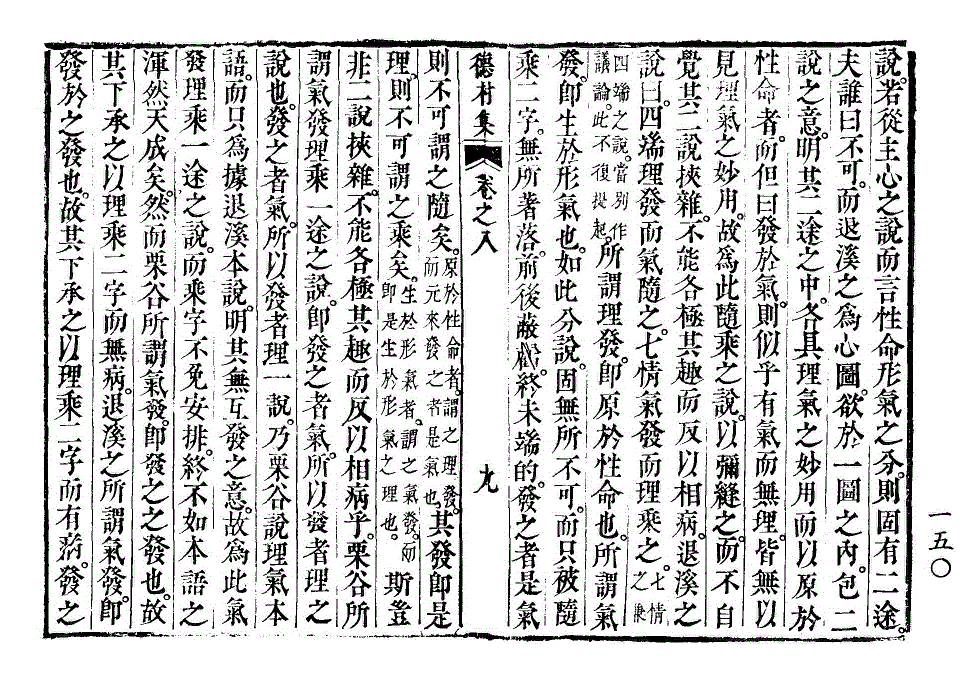 说。若从主心之说而言性命形气之分。则固有二途。夫谁曰不可。而退溪之为心图。欲于一图之内。包二说之意。明其二途之中。各具理气之妙用而以原于性命者。而但曰发于气。则似乎有气而无理。皆无以见理气之妙用。故为此随乘之说。以弥缝之。而不自觉其二说挟杂。不能各极其趣而反以相病。退溪之说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七情之兼四端之说。当别作议论。此不复提起。)所谓理发。即原于性命也。所谓气发。即生于形气也。如此分说。固无所不可。而只被随乘二字。无所著落。前后蔽亏。终未端的。发之者是气则不可谓之随矣。(原于性命者。谓之理发。而元来发之者是气也。)其发即是理。则不可谓之乘矣。(生于形气者。谓之气发。而即是生于形气之理也。)斯岂非二说挟杂。不能各极其趣而反以相病乎。栗谷所谓气发理乘一途之说。即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之说也。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一说。乃栗谷说理气本语。而只为据退溪本说。明其无互发之意。故为此气发理乘一途之说。而乘字不免安排。终不如本语之浑然天成矣。然而栗谷所谓气发。即发之之发也。故其下承之以理乘二字而无病。退溪之所谓气发。即发于之发也。故其下承之以理乘二字而有病。发之
说。若从主心之说而言性命形气之分。则固有二途。夫谁曰不可。而退溪之为心图。欲于一图之内。包二说之意。明其二途之中。各具理气之妙用而以原于性命者。而但曰发于气。则似乎有气而无理。皆无以见理气之妙用。故为此随乘之说。以弥缝之。而不自觉其二说挟杂。不能各极其趣而反以相病。退溪之说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七情之兼四端之说。当别作议论。此不复提起。)所谓理发。即原于性命也。所谓气发。即生于形气也。如此分说。固无所不可。而只被随乘二字。无所著落。前后蔽亏。终未端的。发之者是气则不可谓之随矣。(原于性命者。谓之理发。而元来发之者是气也。)其发即是理。则不可谓之乘矣。(生于形气者。谓之气发。而即是生于形气之理也。)斯岂非二说挟杂。不能各极其趣而反以相病乎。栗谷所谓气发理乘一途之说。即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之说也。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一说。乃栗谷说理气本语。而只为据退溪本说。明其无互发之意。故为此气发理乘一途之说。而乘字不免安排。终不如本语之浑然天成矣。然而栗谷所谓气发。即发之之发也。故其下承之以理乘二字而无病。退溪之所谓气发。即发于之发也。故其下承之以理乘二字而有病。发之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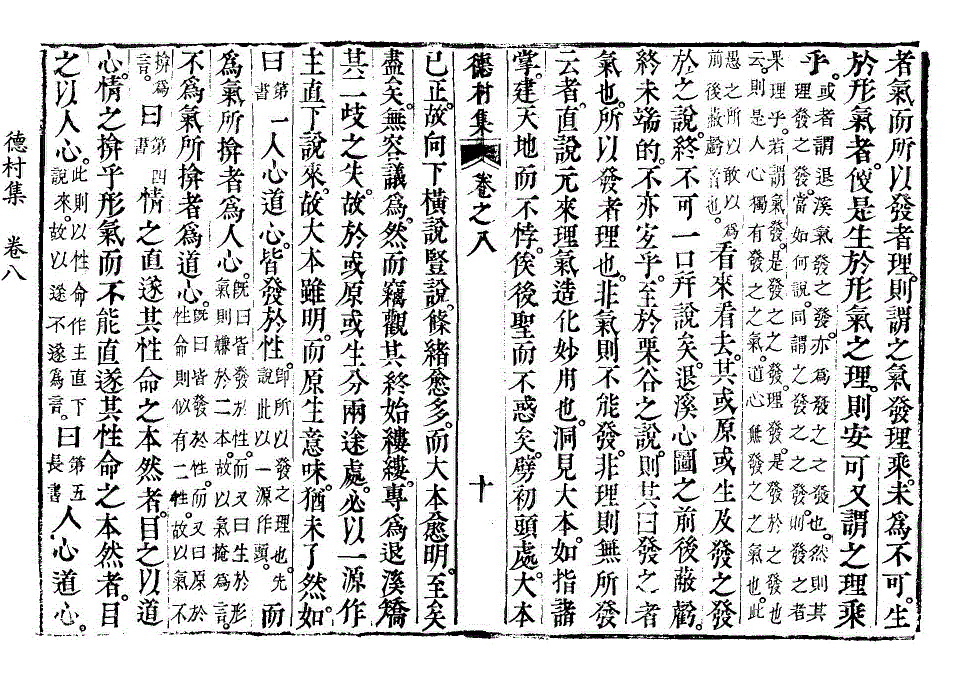 者气而所以发者理。则谓之气发理乘。未为不可。生于形气者。便是生于形气之理。则安可又谓之理乘乎。(或者谓退溪气发之发。亦为发之之发也。然则其理发之发。当如何说。同谓之发之之发。则发之者果理乎。若谓气发。是发之之发。理发。是发于之发也云。则是人心独有发之之气。道心无发之之气也。此愚之所以敢以为前后蔽亏者也。)看来看去。其或原或生及发之发于之说。终不可一口并说矣。退溪心图之前后蔽亏。终未端的。不亦宜乎。至于栗谷之说。则其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云者。直说元来理气造化妙用也。洞见大本。如指诸掌。建天地而不悖。俟后圣而不惑矣。劈初头处。大本已正。故向下横说竖说。条绪愈多。而大本愈明。至矣尽矣。无容议为。然而窃观其终始缕缕。专为退溪矫其二歧之失。故于或原或生分两途处。必以一源作主直下说来。故大本虽明。而原生意味。犹未了然。如曰(第一书)人心道心。皆发于性。(即所以发之理也。先说此以一源作头。)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既曰皆发于性。而又曰生于形气则嫌于二本。故以气掩为言。)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既曰皆发于性。而又曰原于性命则似有二性。故以气不掩为言。)曰(第四书)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此则以性命作主直下说来。故以遂不遂为言。)曰(第五长书)人心道心。
者气而所以发者理。则谓之气发理乘。未为不可。生于形气者。便是生于形气之理。则安可又谓之理乘乎。(或者谓退溪气发之发。亦为发之之发也。然则其理发之发。当如何说。同谓之发之之发。则发之者果理乎。若谓气发。是发之之发。理发。是发于之发也云。则是人心独有发之之气。道心无发之之气也。此愚之所以敢以为前后蔽亏者也。)看来看去。其或原或生及发之发于之说。终不可一口并说矣。退溪心图之前后蔽亏。终未端的。不亦宜乎。至于栗谷之说。则其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云者。直说元来理气造化妙用也。洞见大本。如指诸掌。建天地而不悖。俟后圣而不惑矣。劈初头处。大本已正。故向下横说竖说。条绪愈多。而大本愈明。至矣尽矣。无容议为。然而窃观其终始缕缕。专为退溪矫其二歧之失。故于或原或生分两途处。必以一源作主直下说来。故大本虽明。而原生意味。犹未了然。如曰(第一书)人心道心。皆发于性。(即所以发之理也。先说此以一源作头。)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既曰皆发于性。而又曰生于形气则嫌于二本。故以气掩为言。)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既曰皆发于性。而又曰原于性命则似有二性。故以气不掩为言。)曰(第四书)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此则以性命作主直下说来。故以遂不遂为言。)曰(第五长书)人心道心。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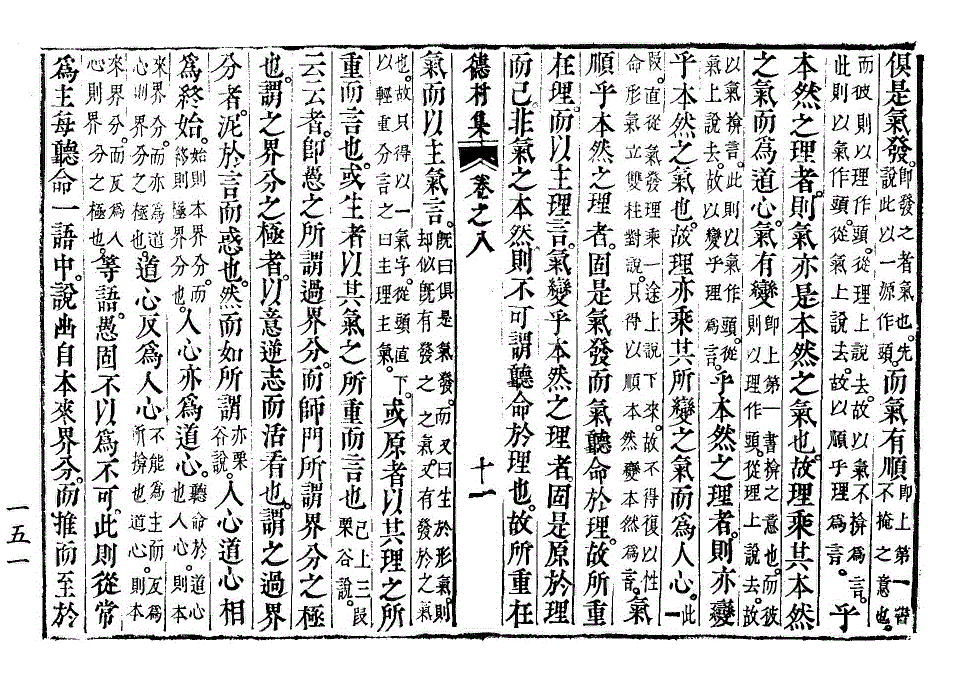 俱是气发。(即发之者气也。先说此以一源作头。)而气有顺(即上第一书不掩之意也。而彼则以理作头。从理上说去。故以气不掩为言。此则以气作头。从气上说去。故以顺乎理为言。)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气有变(即上第一书掩之意也。而彼则以理作头。从理上说去。故以气掩言。此则以气作头。从气上说去。故以变乎理为言。)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此一段。直从气发理乘一途上说下来。故不得复以性命形气立双柱对说。只得以顺本然变本然为言。)气顺乎本然之理者。固是气发而气听命于理。故所重在理。而以主理言。气变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于理而已。非气之本然。则不可谓听命于理也。故所重在气而以主气言。(既曰俱是气发。而又曰生于形气。则却似既有发之之气。又有发于之气也。故只得以一气字。从头直下。以轻重分言之曰主理主气。)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已上三段栗谷说。)云云者。即愚之所谓过界分。而师门所谓界分之极也。谓之界分之极者。以意逆志而活看也。谓之过界分者。泥于言而惑也。然而如所谓(亦栗谷说。)人心道心相为终始。(始则本界分。而终则极界分也。)人心亦为道心。(听命于道心也人心。则本来界分。而亦为道心则界分之极也。)道心反为人心(不能为主而反为所掩也道心。则本来界分。而反为人心则界分之极也。)等语。愚固不以为不可。此则从常为主每听命一语中。说出自本来界分。而推而至于
俱是气发。(即发之者气也。先说此以一源作头。)而气有顺(即上第一书不掩之意也。而彼则以理作头。从理上说去。故以气不掩为言。此则以气作头。从气上说去。故以顺乎理为言。)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气有变(即上第一书掩之意也。而彼则以理作头。从理上说去。故以气掩言。此则以气作头。从气上说去。故以变乎理为言。)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此一段。直从气发理乘一途上说下来。故不得复以性命形气立双柱对说。只得以顺本然变本然为言。)气顺乎本然之理者。固是气发而气听命于理。故所重在理。而以主理言。气变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于理而已。非气之本然。则不可谓听命于理也。故所重在气而以主气言。(既曰俱是气发。而又曰生于形气。则却似既有发之之气。又有发于之气也。故只得以一气字。从头直下。以轻重分言之曰主理主气。)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已上三段栗谷说。)云云者。即愚之所谓过界分。而师门所谓界分之极也。谓之界分之极者。以意逆志而活看也。谓之过界分者。泥于言而惑也。然而如所谓(亦栗谷说。)人心道心相为终始。(始则本界分。而终则极界分也。)人心亦为道心。(听命于道心也人心。则本来界分。而亦为道心则界分之极也。)道心反为人心(不能为主而反为所掩也道心。则本来界分。而反为人心则界分之极也。)等语。愚固不以为不可。此则从常为主每听命一语中。说出自本来界分。而推而至于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2H 页
 界分之极也。掩不掩遂不遂变不变等语。到此方始衬贴。随处发明。无所不可。今则直以不为气所掩而变乎性命之本然者。谓之人心。若据本来界分而言。则道心直原性命。不犯形气。初不可以不掩言也。人心自是生于形气。掩之一字。著不可得矣。且道心以恐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也。故曰微。今已直遂矣。何微之有。人心以易炽而流于恶。故曰危。今已变乎本然。则已流于恶矣。岂但危而已哉。若据界分之极而言。则所谓为气所掩而不能直遂者。正是道心之反为人心也。以道心之反为人心。而直谓之人心可矣。且只举道心。而遗却人心。亦可乎。愚所谓原生意味。犹未了然者此也。愚者之惑。亦不为无理矣。虽然。抑又思之。非界分之过也。恐是立论之高也。今若抽身直出性情窠臼上一层。立于天地造化中(人心听命于道心者。性情窠臼中说也。气听于理者。天地造化中说也。且以人心之生于形气。而不曰生而曰掩者。恐是天地造化中说也。)俯看。则以人心为掩于气。为不能直遂。为变乎本然。未或不可。盖天地造化中。曷尝有形气。来到得气以成形。方是为人。谓之掩。谓之不能直遂。谓之变乎本然。亦宜矣。然而其柰今日之论。便从人生而静以下说。何哉。岂可如此悬空过高。不贴之吾身
界分之极也。掩不掩遂不遂变不变等语。到此方始衬贴。随处发明。无所不可。今则直以不为气所掩而变乎性命之本然者。谓之人心。若据本来界分而言。则道心直原性命。不犯形气。初不可以不掩言也。人心自是生于形气。掩之一字。著不可得矣。且道心以恐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也。故曰微。今已直遂矣。何微之有。人心以易炽而流于恶。故曰危。今已变乎本然。则已流于恶矣。岂但危而已哉。若据界分之极而言。则所谓为气所掩而不能直遂者。正是道心之反为人心也。以道心之反为人心。而直谓之人心可矣。且只举道心。而遗却人心。亦可乎。愚所谓原生意味。犹未了然者此也。愚者之惑。亦不为无理矣。虽然。抑又思之。非界分之过也。恐是立论之高也。今若抽身直出性情窠臼上一层。立于天地造化中(人心听命于道心者。性情窠臼中说也。气听于理者。天地造化中说也。且以人心之生于形气。而不曰生而曰掩者。恐是天地造化中说也。)俯看。则以人心为掩于气。为不能直遂。为变乎本然。未或不可。盖天地造化中。曷尝有形气。来到得气以成形。方是为人。谓之掩。谓之不能直遂。谓之变乎本然。亦宜矣。然而其柰今日之论。便从人生而静以下说。何哉。岂可如此悬空过高。不贴之吾身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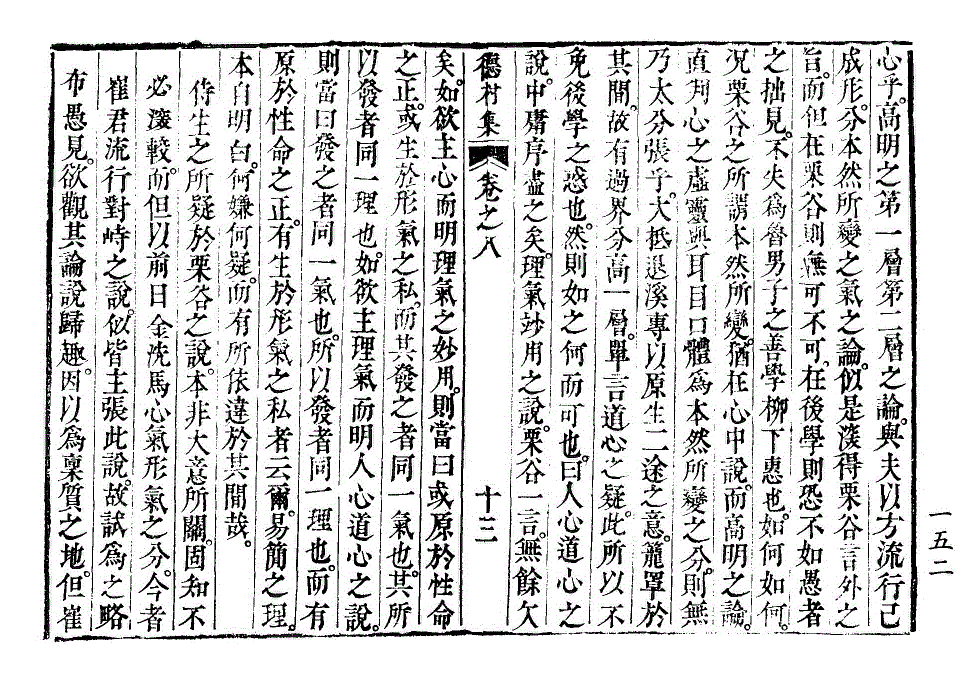 心乎。高明之第一层第二层之论。与夫以方流行已成形。分本然所变之气之论。似是深得栗谷言外之旨。而但在栗谷则无可不可。在后学则恐不如愚者之拙见。不失为鲁男子之善学柳下惠也。如何如何。况栗谷之所谓本然所变。犹在心中说。而高明之论。直判心之虚灵与耳目口体为本然所变之分。则无乃太分张乎。大抵退溪专以原生二途之意。笼罩于其间。故有过界分高一层。单言道心之疑。此所以不免后学之惑也。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人心道心之说。中庸序尽之矣。理气妙用之说。栗谷一言。无馀欠矣。如欲主心而明理气之妙用。则当曰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而其发之者同一气也。其所以发者同一理也。如欲主理气而明人心道心之说。则当曰发之者同一气也。所以发者同一理也。而有原于性命之正。有生于形气之私者云尔。易简之理。本自明白。何嫌何疑。而有所依违于其间哉。
心乎。高明之第一层第二层之论。与夫以方流行已成形。分本然所变之气之论。似是深得栗谷言外之旨。而但在栗谷则无可不可。在后学则恐不如愚者之拙见。不失为鲁男子之善学柳下惠也。如何如何。况栗谷之所谓本然所变。犹在心中说。而高明之论。直判心之虚灵与耳目口体为本然所变之分。则无乃太分张乎。大抵退溪专以原生二途之意。笼罩于其间。故有过界分高一层。单言道心之疑。此所以不免后学之惑也。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人心道心之说。中庸序尽之矣。理气妙用之说。栗谷一言。无馀欠矣。如欲主心而明理气之妙用。则当曰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而其发之者同一气也。其所以发者同一理也。如欲主理气而明人心道心之说。则当曰发之者同一气也。所以发者同一理也。而有原于性命之正。有生于形气之私者云尔。易简之理。本自明白。何嫌何疑。而有所依违于其间哉。侍生之所疑于栗谷之说。本非大意所关。固知不必深较。而但以前日金洗马心气形气之分。今者崔君流行对峙之说。似皆主张此说。故试为之略布愚见。欲观其论说归趣。因以为禀质之地。但崔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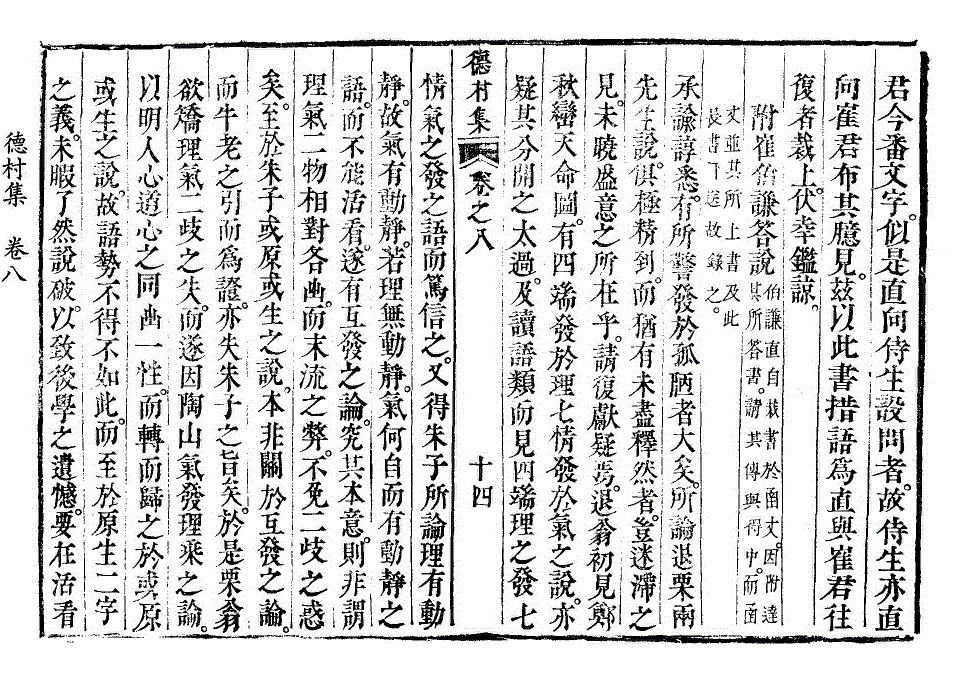 君今番文字。似是直向侍生设问者。故侍生亦直向崔君布其臆见。玆以此书措语为直与崔君往复者裁上。伏幸鉴谅。
君今番文字。似是直向侍生设问者。故侍生亦直向崔君布其臆见。玆以此书措语为直与崔君往复者裁上。伏幸鉴谅。附崔伯谦答说 伯谦直自栽(一作裁)书于函丈。因附达其所答书。请其传与得中。而函丈并其所上书及此长书下送故录之。
承谕谆悉。有所警发于孤陋者大矣。所论退栗两先生说。俱极精到。而犹有未尽释然者。岂迷滞之见。未晓盛意之所在乎。请复献疑焉。退翁初见郑秋峦天命图。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说。亦疑其分开之太过。及读语类而见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之语而笃信之。又得朱子所论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之语。而不能活看。遂有互发之论。究其本意。则非谓理气二物相对各出。而末流之弊。不免二歧之惑矣。至于朱子或原或生之说。本非关于互发之论。而牛老之引而为證。亦失朱子之旨矣。于是栗翁欲矫理气二歧之失。而遂因陶山气发理乘之论。以明人心道心之同出一性。而转而归之于或原或生之说。故语势不得不如此。而至于原生二字之义。未暇了然说破。以致后学之遗憾。要在活看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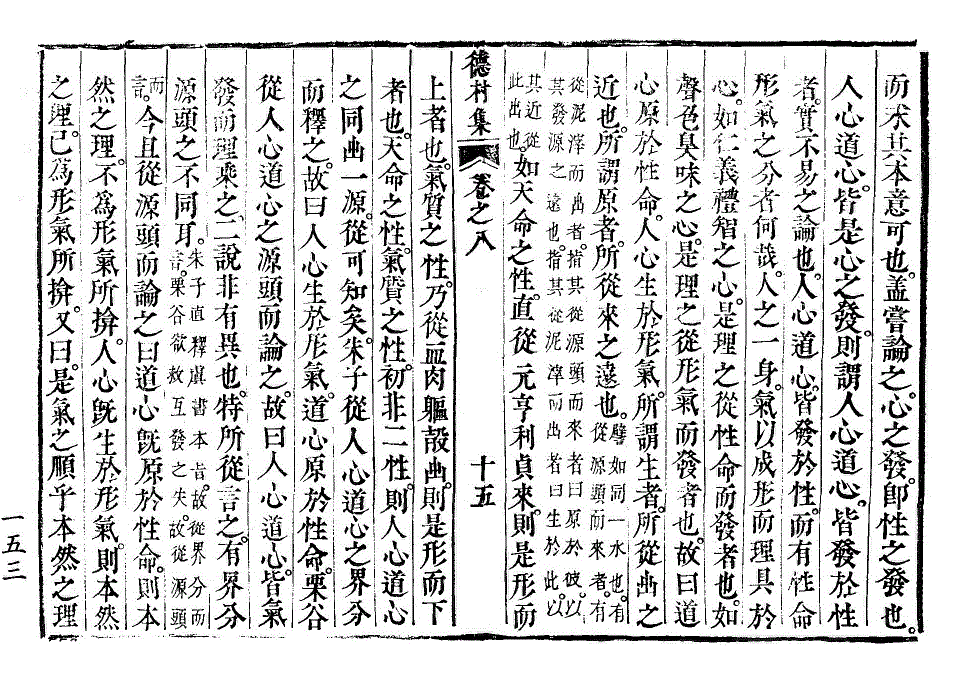 而求其本意可也。盖尝论之。心之发。即性之发也。人心道心。皆是心之发。则谓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者。实不易之论也。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有性命形气之分者何哉。人之一身。气以成形而理具于心。如仁义礼智之心。是理之从性命而发者也。如声色臭味之心。是理之从形气而发者也。故曰道心原于性命。人心生于形气。所谓生者。所从出之近也。所谓原者。所从来之远也。(譬如同一水也。有从源头而来者。有从泥滓而出者。指其从源头而来者曰原于彼。以其发源之远也。指其从泥滓而出者曰生于此。以其近从此出也。)如天命之性。直从元亨利贞来。则是形而上者也。气质之性。乃从血肉躯㱿出。则是形而下者也。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初非二性。则人心道心之同出一源。从可知矣。朱子从人心道心之界分而释之。故曰人心生于形气。道心原于性命。栗谷从人心道心之源头而论之。故曰人心道心。皆气发而理乘之。二说非有异也。特所从言之。有界分源头之不同耳。(朱子直释虞书本旨。故从界分而言。栗谷欲救互发之失。故从源头而言。)今且从源头而论之曰道心既原于性命。则本然之理。不为形气所掩。人心既生于形气。则本然之理。已为形气所掩。又曰。是气之顺乎本然之理
而求其本意可也。盖尝论之。心之发。即性之发也。人心道心。皆是心之发。则谓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者。实不易之论也。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有性命形气之分者何哉。人之一身。气以成形而理具于心。如仁义礼智之心。是理之从性命而发者也。如声色臭味之心。是理之从形气而发者也。故曰道心原于性命。人心生于形气。所谓生者。所从出之近也。所谓原者。所从来之远也。(譬如同一水也。有从源头而来者。有从泥滓而出者。指其从源头而来者曰原于彼。以其发源之远也。指其从泥滓而出者曰生于此。以其近从此出也。)如天命之性。直从元亨利贞来。则是形而上者也。气质之性。乃从血肉躯㱿出。则是形而下者也。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初非二性。则人心道心之同出一源。从可知矣。朱子从人心道心之界分而释之。故曰人心生于形气。道心原于性命。栗谷从人心道心之源头而论之。故曰人心道心。皆气发而理乘之。二说非有异也。特所从言之。有界分源头之不同耳。(朱子直释虞书本旨。故从界分而言。栗谷欲救互发之失。故从源头而言。)今且从源头而论之曰道心既原于性命。则本然之理。不为形气所掩。人心既生于形气。则本然之理。已为形气所掩。又曰。是气之顺乎本然之理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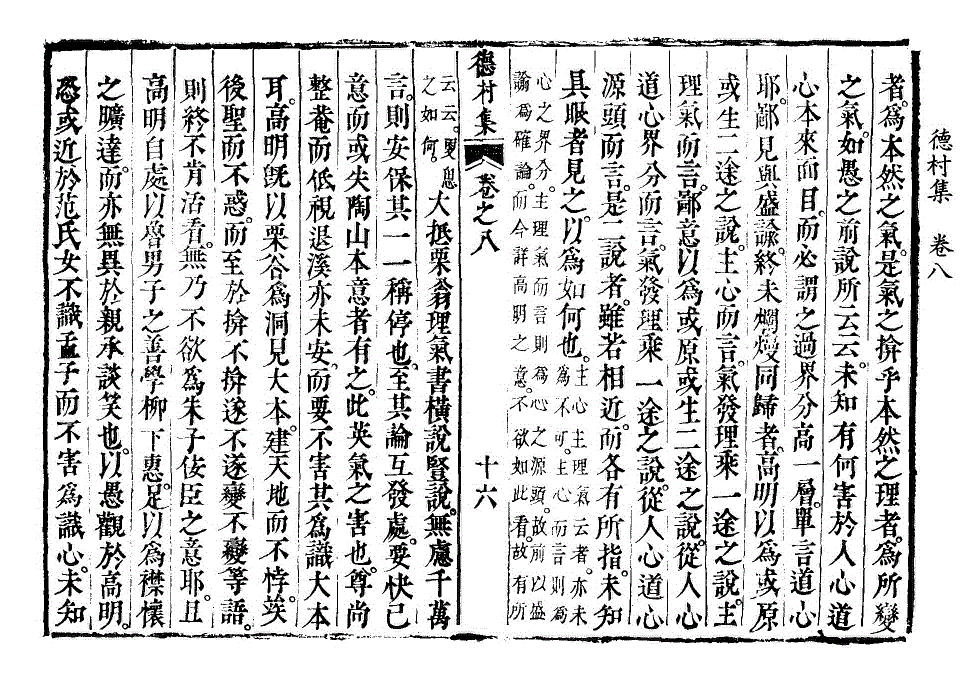 者。为本然之气。是气之掩乎本然之理者。为所变之气。如愚之前说所云云。未知有何害于人心道心本来面目。而必谓之过界分高一层。单言道心耶。鄙见与盛谕。终未烂熳同归者。高明以为或原或生二途之说。主心而言。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主理气而言。鄙意以为或原或生二途之说。从人心道心界分而言。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从人心道心源头而言。是二说者。虽若相近。而各有所指。未知具眼者见之。以为如何也。(主心主理气云者。亦未为不可。主心而言则为心之界分。主理气而言则为心之源头。故前以盛谕为确论。而今详高明之意。不欲如此看。故有所云云。更思之如何。)大抵栗翁理气书横说竖说。无虑千万言。则安保其一一称停也。至其论互发处。要快己意而或失陶山本意者有之。此英气之害也。尊尚整庵而低视退溪亦未安。而要不害其为识大本耳。高明既以栗谷为洞见大本。建天地而不悖。俟后圣而不惑。而至于掩不掩遂不遂变不变等语。则终不肯活看。无乃不欲为朱子佞臣之意耶。且高明自处以鲁男子之善学柳下惠。足以为襟怀之旷达。而亦无异于亲承谈笑也。以愚观于高明。恐或近于范氏女不识孟子而不害为识心。未知
者。为本然之气。是气之掩乎本然之理者。为所变之气。如愚之前说所云云。未知有何害于人心道心本来面目。而必谓之过界分高一层。单言道心耶。鄙见与盛谕。终未烂熳同归者。高明以为或原或生二途之说。主心而言。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主理气而言。鄙意以为或原或生二途之说。从人心道心界分而言。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从人心道心源头而言。是二说者。虽若相近。而各有所指。未知具眼者见之。以为如何也。(主心主理气云者。亦未为不可。主心而言则为心之界分。主理气而言则为心之源头。故前以盛谕为确论。而今详高明之意。不欲如此看。故有所云云。更思之如何。)大抵栗翁理气书横说竖说。无虑千万言。则安保其一一称停也。至其论互发处。要快己意而或失陶山本意者有之。此英气之害也。尊尚整庵而低视退溪亦未安。而要不害其为识大本耳。高明既以栗谷为洞见大本。建天地而不悖。俟后圣而不惑。而至于掩不掩遂不遂变不变等语。则终不肯活看。无乃不欲为朱子佞臣之意耶。且高明自处以鲁男子之善学柳下惠。足以为襟怀之旷达。而亦无异于亲承谈笑也。以愚观于高明。恐或近于范氏女不识孟子而不害为识心。未知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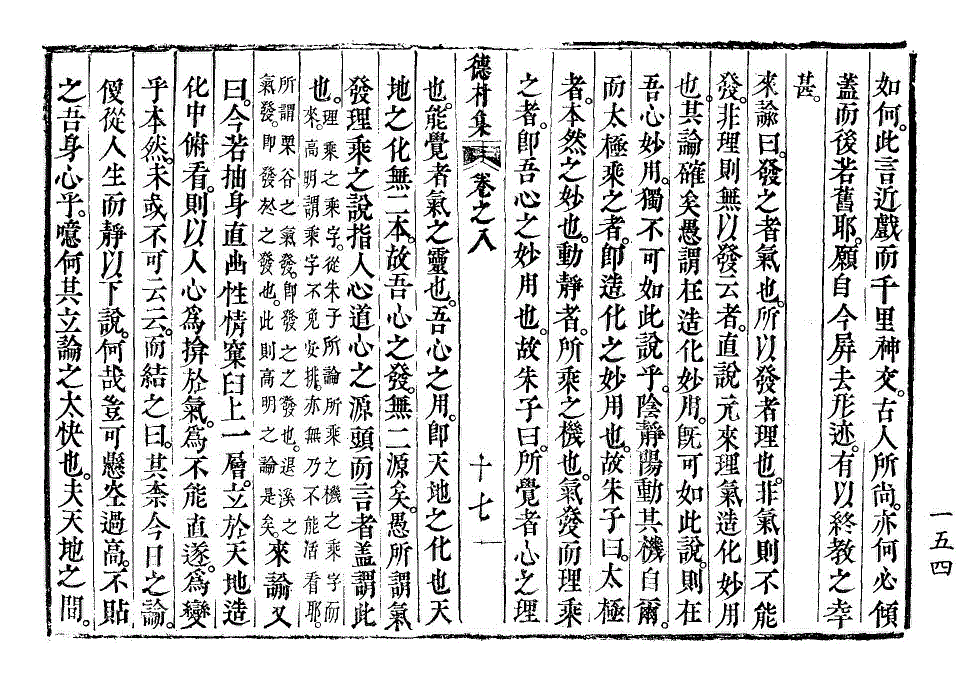 如何。此言近戏而千里神交。古人所尚。亦何必倾盖而后若旧耶。愿自今屏去形迹。有以终教之幸甚。
如何。此言近戏而千里神交。古人所尚。亦何必倾盖而后若旧耶。愿自今屏去形迹。有以终教之幸甚。来谕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以发云者。直说元来理气造化妙用也。其论确矣愚谓在造化妙用。既可如此说。则在吾心妙用。独不可如此说乎。阴静阳动其机自尔。而太极乘之者。即造化之妙用也。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气发而理乘之者。即吾心之妙用也。故朱子曰。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吾心之用。即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无二本。故吾心之发。无二源矣。愚所谓气发理乘之说指人心道心之源头而言者盖谓此也。(理乘之乘字。从朱子所论所乘之机之乘字而来。高明谓乘字不免安排。亦无乃不能活看耶。所谓栗谷之气发。即发之之发也。退溪之气发。即发于之发也。此则高明之论是矣。)来谕又曰。今若抽身直出性情窠臼上一层。立于天地造化中俯看。则以人心为掩于气。为不能直遂。为变乎本然。未或不可云云。而结之曰。其柰今日之论。便从人生而静以下说。何哉岂可悬空过高。不贴之吾身心乎。噫何其立论之太快也。夫天地之间。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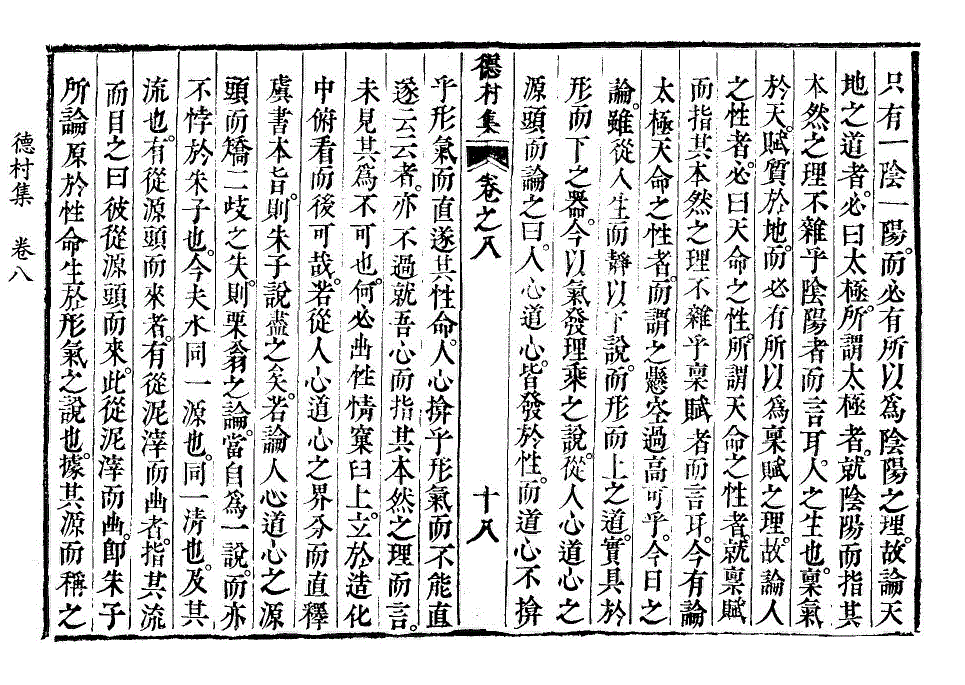 只有一阴一阳。而必有所以为阴阳之理。故论天地之道者。必曰太极。所谓太极者。就阴阳而指其本然之理不杂乎阴阳者而言耳。人之生也。禀气于天。赋质于地。而必有所以为禀赋之理。故论人之性者。必曰天命之性。所谓天命之性者。就禀赋而指其本然之理不杂乎禀赋者而言耳。今有论太极天命之性者。而谓之悬空过高可乎。今日之论。虽从人生而静以下说。而形而上之道。实具于形而下之器。今以气发理乘之说。从人心道心之源头而论之曰。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道心不掩乎形气而直遂其性命。人心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云云者。亦不过就吾心而指其本然之理而言。未见其为不可也。何必出性情窠臼上。立于造化中俯看而后可哉。若从人心道心之界分而直释虞书本旨。则朱子说尽之矣。若论人心道心之源头而矫二歧之失。则栗翁之论。当自为一说。而亦不悖于朱子也。今夫水同一源也。同一清也。及其流也。有从源头而来者。有从泥滓而出者。指其流而目之曰彼从源头而来。此从泥滓而出。即朱子所论原于性命生于形气之说也。据其源而称之
只有一阴一阳。而必有所以为阴阳之理。故论天地之道者。必曰太极。所谓太极者。就阴阳而指其本然之理不杂乎阴阳者而言耳。人之生也。禀气于天。赋质于地。而必有所以为禀赋之理。故论人之性者。必曰天命之性。所谓天命之性者。就禀赋而指其本然之理不杂乎禀赋者而言耳。今有论太极天命之性者。而谓之悬空过高可乎。今日之论。虽从人生而静以下说。而形而上之道。实具于形而下之器。今以气发理乘之说。从人心道心之源头而论之曰。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道心不掩乎形气而直遂其性命。人心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云云者。亦不过就吾心而指其本然之理而言。未见其为不可也。何必出性情窠臼上。立于造化中俯看而后可哉。若从人心道心之界分而直释虞书本旨。则朱子说尽之矣。若论人心道心之源头而矫二歧之失。则栗翁之论。当自为一说。而亦不悖于朱子也。今夫水同一源也。同一清也。及其流也。有从源头而来者。有从泥滓而出者。指其流而目之曰彼从源头而来。此从泥滓而出。即朱子所论原于性命生于形气之说也。据其源而称之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5L 页
 曰。彼直从源头而来。不犯泥滓。故保其本然之清。此虽从源头而来。已犯泥滓。故不能保其本然之清。即栗翁所论不掩于形气而直遂。掩于形气而不能直遂之说也。高明不各求其本意。直以朱子之说。准栗谷之说曰道心不掩形气。初不可以不掩言。人心本生于形气。掩之一字。著不可得。此区区所以不能无惑者也。大抵义理之学。精微之奥。必须精察而明辨之。圣贤之言。或异或同。或离或合。各有归趣。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就异中而见其有同。分而为二。而不害其未尝离。合而为一。而实归于不相杂者。非朱门之要法而退陶之所发明者耶。○乃敢以立论太快。奉讥于高明。而所自为说。又不免此病。真所谓不见其睫者也。想复发一笑焉。
曰。彼直从源头而来。不犯泥滓。故保其本然之清。此虽从源头而来。已犯泥滓。故不能保其本然之清。即栗翁所论不掩于形气而直遂。掩于形气而不能直遂之说也。高明不各求其本意。直以朱子之说。准栗谷之说曰道心不掩形气。初不可以不掩言。人心本生于形气。掩之一字。著不可得。此区区所以不能无惑者也。大抵义理之学。精微之奥。必须精察而明辨之。圣贤之言。或异或同。或离或合。各有归趣。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就异中而见其有同。分而为二。而不害其未尝离。合而为一。而实归于不相杂者。非朱门之要法而退陶之所发明者耶。○乃敢以立论太快。奉讥于高明。而所自为说。又不免此病。真所谓不见其睫者也。想复发一笑焉。答崔伯谦书(戊戌)
讲服盛名。盖已久矣。昔年。权友奉致盛说一篇于函丈。函丈令得中与之往复。以究其说。盖欲因而观得中见识之所到然后为之折衷也。得中窃自幸其以平日慕仰之心。而得与之上下其论。又幸其释疑辨惑之有地。遂承教而不辞。执事者乃不以卑鄙。辱与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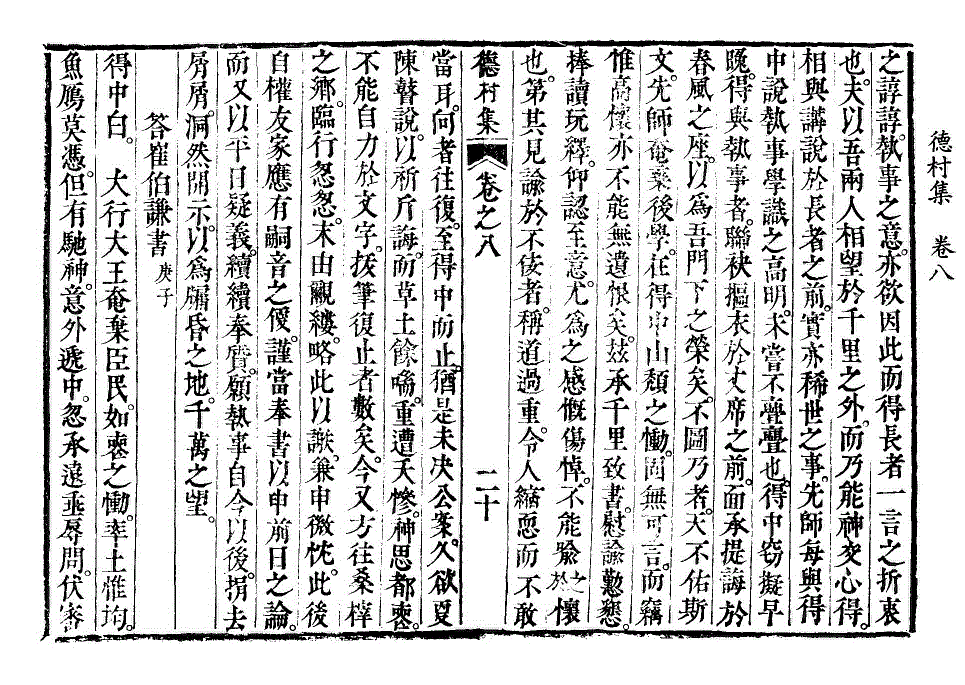 之谆谆。执事之意。亦欲因此而得长者一言之折衷也。夫以吾两人相望于千里之外。而乃能神交心得。相与讲说于长者之前。实亦稀世之事。先师每与得中说执事学识之高明。未尝不亹亹也。得中窃拟早晚。得与执事者。联袂抠衣于丈席之前。面承提诲于春风之座。以为吾门下之荣矣。不图乃者。天不佑斯文。先师奄弃后学。在得中山颓之恸。固无可言。而窃惟高怀亦不能无遗恨矣。玆承千里致书。慰谕勤恳。捧读玩绎。仰认至意。尤为之感慨伤悼。不能喻之于怀也。第其见谕于不佞者。称道过重。令人缩恧而不敢当耳。向者往复。至得中而止。犹是未决公案。久欲更陈瞽说。以祈斤诲。而草土馀喘。重遭夭惨。神思都丧。不能自力于文字。拔笔复止者数矣。今又方往桑梓之乡。临行匆匆。末由覼缕。略此以𧬄。兼申微忱。此后自权友家应有嗣音之便。谨当奉书以申前日之论。而又以平日疑义。续续奉质。愿执事自今以后。捐去屑屑。洞然开示。以为牖昏之地。千万之望。
之谆谆。执事之意。亦欲因此而得长者一言之折衷也。夫以吾两人相望于千里之外。而乃能神交心得。相与讲说于长者之前。实亦稀世之事。先师每与得中说执事学识之高明。未尝不亹亹也。得中窃拟早晚。得与执事者。联袂抠衣于丈席之前。面承提诲于春风之座。以为吾门下之荣矣。不图乃者。天不佑斯文。先师奄弃后学。在得中山颓之恸。固无可言。而窃惟高怀亦不能无遗恨矣。玆承千里致书。慰谕勤恳。捧读玩绎。仰认至意。尤为之感慨伤悼。不能喻之于怀也。第其见谕于不佞者。称道过重。令人缩恧而不敢当耳。向者往复。至得中而止。犹是未决公案。久欲更陈瞽说。以祈斤诲。而草土馀喘。重遭夭惨。神思都丧。不能自力于文字。拔笔复止者数矣。今又方往桑梓之乡。临行匆匆。末由覼缕。略此以𧬄。兼申微忱。此后自权友家应有嗣音之便。谨当奉书以申前日之论。而又以平日疑义。续续奉质。愿执事自今以后。捐去屑屑。洞然开示。以为牖昏之地。千万之望。答崔伯谦书(庚子)
得中白。 大行大王奄弃臣民。如丧之恸。率土惟均。鱼雁莫凭。但有驰神。意外递中。忽承远垂辱问。伏审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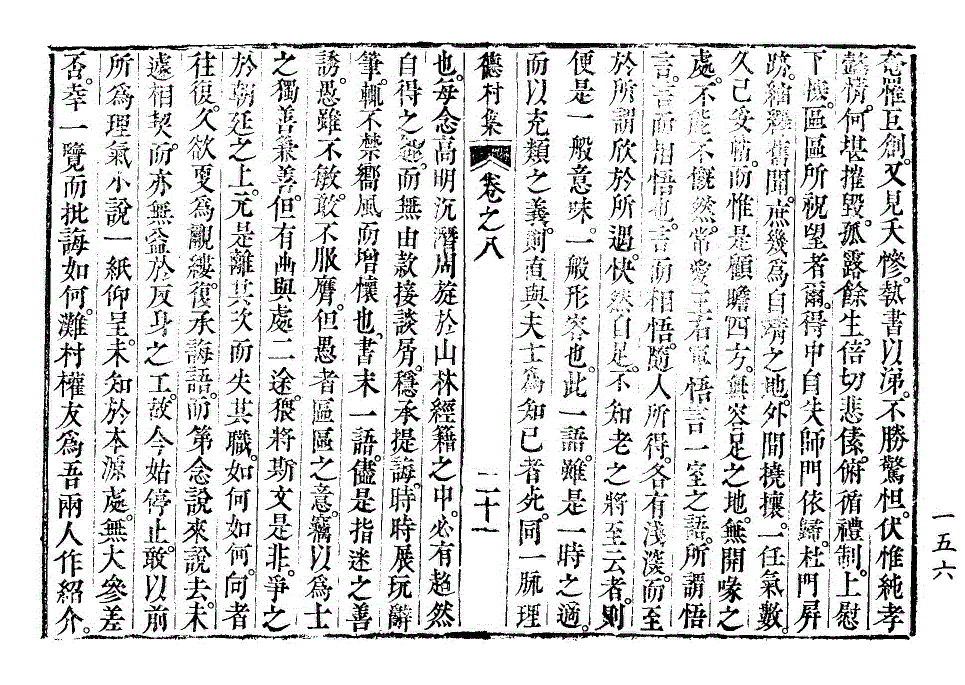 奄罹巨创。又见夭惨。执书以涕。不胜惊怛。伏惟纯孝懿情。何堪摧毁。孤露馀生。倍切悲傃。俯循礼制。上慰下抚。区区所祝望者尔。得中自失师门依归。杜门屏迹。䌷绎旧闻。庶几为自靖之地。外间挠攘。一任气数。久已妥帖。而惟是顾瞻四方。无容足之地。无开喙之处。不能不慨然。常爱王右军悟言一室之语。所谓悟言。言而相悟也。言而相悟。随人所得。各有浅深。而至于所谓欣于所遇。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云者。则便是一般意味。一般形容也。此一语。虽是一时之适。而以充类之义。则直与夫士为知己者死。同一脉理也。每念高明沉潜周旋于山林经籍之中。必有超然自得之趣。而无由款接谈屑。稳承提诲。时时展玩辞笔。辄不禁向风而增怀也。书末一语。尽是指迷之善诱。愚虽不敏。敢不服膺。但愚者区区之意。窃以为士之独善兼善。但有出与处二途。猥将斯文是非。争之于朝廷之上。元是离其次而失其职。如何如何。向者往复。久欲更为覼缕。复承诲语。而第念说来说去。未遽相契。而亦无益于反身之工。故今姑停止。敢以前所为理气小说一纸仰呈。未知于本源处。无大参差否。幸一览而批诲如何。滩村权友为吾两人作绍介。
奄罹巨创。又见夭惨。执书以涕。不胜惊怛。伏惟纯孝懿情。何堪摧毁。孤露馀生。倍切悲傃。俯循礼制。上慰下抚。区区所祝望者尔。得中自失师门依归。杜门屏迹。䌷绎旧闻。庶几为自靖之地。外间挠攘。一任气数。久已妥帖。而惟是顾瞻四方。无容足之地。无开喙之处。不能不慨然。常爱王右军悟言一室之语。所谓悟言。言而相悟也。言而相悟。随人所得。各有浅深。而至于所谓欣于所遇。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云者。则便是一般意味。一般形容也。此一语。虽是一时之适。而以充类之义。则直与夫士为知己者死。同一脉理也。每念高明沉潜周旋于山林经籍之中。必有超然自得之趣。而无由款接谈屑。稳承提诲。时时展玩辞笔。辄不禁向风而增怀也。书末一语。尽是指迷之善诱。愚虽不敏。敢不服膺。但愚者区区之意。窃以为士之独善兼善。但有出与处二途。猥将斯文是非。争之于朝廷之上。元是离其次而失其职。如何如何。向者往复。久欲更为覼缕。复承诲语。而第念说来说去。未遽相契。而亦无益于反身之工。故今姑停止。敢以前所为理气小说一纸仰呈。未知于本源处。无大参差否。幸一览而批诲如何。滩村权友为吾两人作绍介。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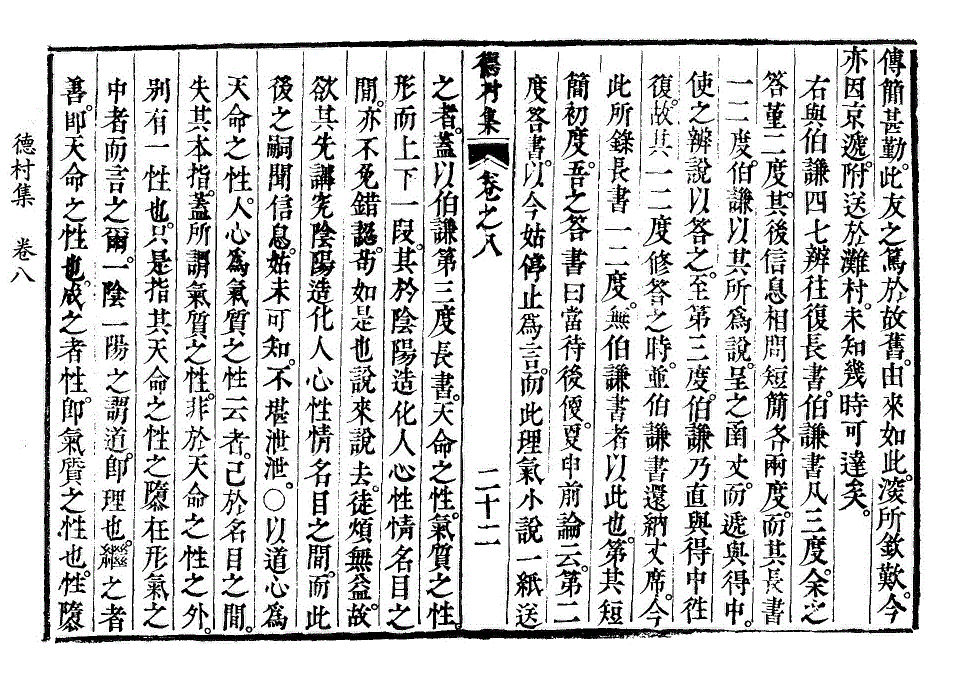 传简甚勤。此友之笃于故旧。由来如此。深所钦叹。今亦因京递。附送于滩村。未知几时可达矣。
传简甚勤。此友之笃于故旧。由来如此。深所钦叹。今亦因京递。附送于滩村。未知几时可达矣。右与伯谦四七辨往复长书。伯谦书凡三度。余之答堇二度。其后信息相问短简各两度。而其长书一二度。伯谦以其所为说。呈之函丈。而递与得中。使之辨说以答之。至第三度。伯谦乃直与得中往复。故其一二度修答之时。并伯谦书还纳丈席。今此所录长书一二度。无伯谦书者以此也。第其短简初度。吾之答书曰当待后便。更申前论云。第二度答书。以今姑停止为言。而此理气小说一纸送之者。盖以伯谦第三度长书。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形而上下一段。其于阴阳造化人心性情名目之间。亦不免错认。苟如是也说来说去。徒烦无益。故欲其先讲究阴阳造化人心性情名目之间。而此后之嗣闻信息。姑未可知。不堪泄泄。○以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云者。已于名目之间。失其本指。盖所谓气质之性。非于天命之性之外。别有一性也。只是指其天命之性之隳在形气之中者而言之尔。一阴一阳之谓道。即理也。继之者善。即天命之性也。成之者性。即气质之性也。性隳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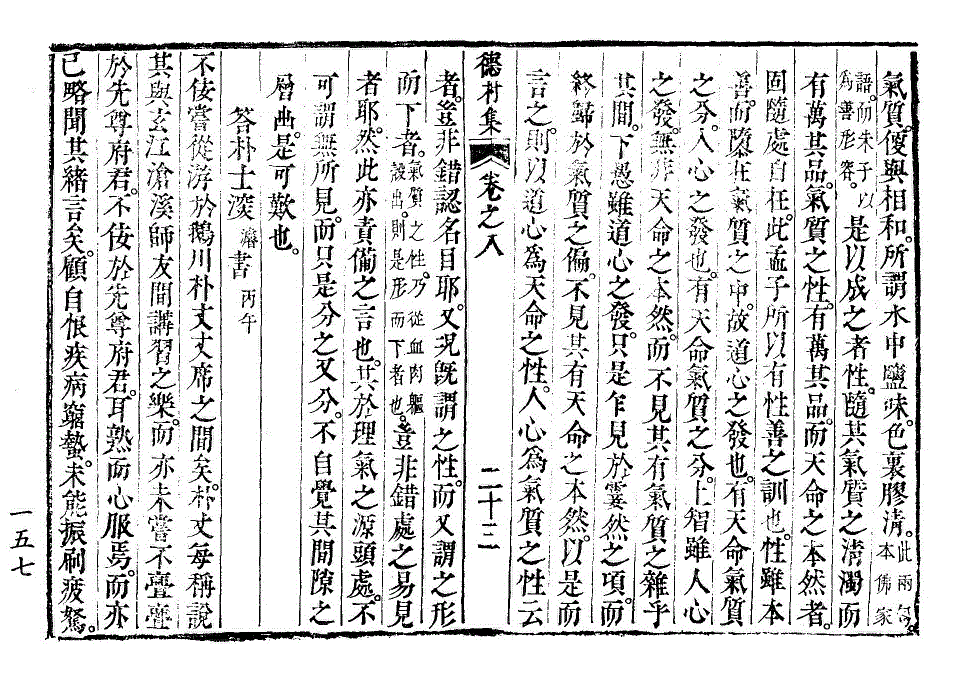 气质。便与相和。所谓水中盐味。色里胶清。(此两句。本佛家语。而朱子以为善形容。)是以成之者性。随其气质之清浊而有万其品。气质之性。有万其品。而天命之本然者。固随处自在。此孟子所以有性善之训也。性虽本善。而隳在气质之中。故道心之发也。有天命气质之分。人心之发也。有天命气质之分。上智虽人心之发。无非天命之本然。而不见其有气质之杂乎其间。下愚虽道心之发。只是乍见于霎然之顷。而终归于气质之偏。不见其有天命之本然。以是而言之。则以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云者。岂非错认名目耶。又况既谓之性。而又谓之形而下者。(气质之性。乃从血肉躯壳出。则是形而下者也。)岂非错处之易见者耶。然此亦责备之言也。其于理气之源头处。不可谓无所见。而只是分之又分。不自觉其间隙之层出。是可叹也。
气质。便与相和。所谓水中盐味。色里胶清。(此两句。本佛家语。而朱子以为善形容。)是以成之者性。随其气质之清浊而有万其品。气质之性。有万其品。而天命之本然者。固随处自在。此孟子所以有性善之训也。性虽本善。而隳在气质之中。故道心之发也。有天命气质之分。人心之发也。有天命气质之分。上智虽人心之发。无非天命之本然。而不见其有气质之杂乎其间。下愚虽道心之发。只是乍见于霎然之顷。而终归于气质之偏。不见其有天命之本然。以是而言之。则以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云者。岂非错认名目耶。又况既谓之性。而又谓之形而下者。(气质之性。乃从血肉躯壳出。则是形而下者也。)岂非错处之易见者耶。然此亦责备之言也。其于理气之源头处。不可谓无所见。而只是分之又分。不自觉其间隙之层出。是可叹也。答朴士深(浚)书(丙午)
不佞尝从游于鹅川朴丈丈席之间矣。朴丈每称说其与玄江沧溪师友间讲习之乐。而亦未尝不亹亹于先尊府君。不佞于先尊府君。耳熟而心服焉。而亦已略闻其绪言矣。顾自恨疾病穷蛰。未能振刷疲驽。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8H 页
 趋下风而望馀光也。及今既失师门依归。伥伥然靡所底止。回想沧溪鹅川交游之地。亦复寂寥荒凉。无以寻其坠绪。居常感慨。永言兴怀而已。向者逆旅邂逅。殆是天与其便。而望见容仪。浑然端厚。奉接辞气。蔼然和雅。虽造次匆卒。未暇深叩。而于眉宇之间。想得其所存。有以信其不失世守之正。归来充然。若有所得。不谓乃者忽蒙眷惠手翰。垂意勤挚。且以平日疑义见示。以开讲论之端。仰认足下相与之义甚厚。三复感叹。不任微情。而自顾浅陋何以获此。且悚且惭。亦不自胜。俯询诸说。谨以别纸奉答。平日看文字。本不会究索。承问之后。乃觉其从前不曾致思。泛泛看过。始乃翻阅书册。逐段参考。敢以臆见覼缕而求教。丽泽之资。已得于倾盖之初。有如是矣。若得遂蒙开释。俾有归一之地。则其为孤陋之幸。胡可胜言。
趋下风而望馀光也。及今既失师门依归。伥伥然靡所底止。回想沧溪鹅川交游之地。亦复寂寥荒凉。无以寻其坠绪。居常感慨。永言兴怀而已。向者逆旅邂逅。殆是天与其便。而望见容仪。浑然端厚。奉接辞气。蔼然和雅。虽造次匆卒。未暇深叩。而于眉宇之间。想得其所存。有以信其不失世守之正。归来充然。若有所得。不谓乃者忽蒙眷惠手翰。垂意勤挚。且以平日疑义见示。以开讲论之端。仰认足下相与之义甚厚。三复感叹。不任微情。而自顾浅陋何以获此。且悚且惭。亦不自胜。俯询诸说。谨以别纸奉答。平日看文字。本不会究索。承问之后。乃觉其从前不曾致思。泛泛看过。始乃翻阅书册。逐段参考。敢以臆见覼缕而求教。丽泽之资。已得于倾盖之初。有如是矣。若得遂蒙开释。俾有归一之地。则其为孤陋之幸。胡可胜言。别纸
问。地道以右为尊。则家庙当立于正寝之西。而乃立于正寝之东。未知其意。
按礼记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集说曰。右阴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阳也。人道所乡。故左宗庙。位宗庙于人道所乡。亦不死其亲之义。甘誓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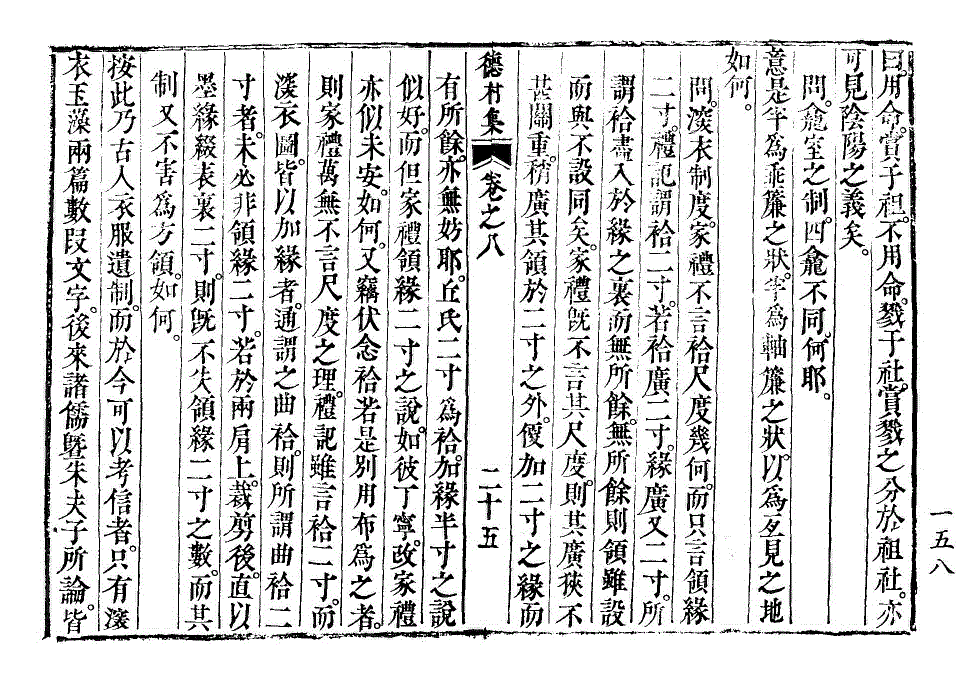 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赏戮之分于祖社。亦可见阴阳之义矣。
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赏戮之分于祖社。亦可见阴阳之义矣。问。龛室之制。四龛不同。何耶。
意是半为垂帘之状。半为轴帘之状。以为互见之地如何。
问。深衣制度。家礼不言袷尺度几何。而只言领缘二寸。礼记谓袷二寸。若袷广二寸。缘广又二寸。所谓袷尽入于缘之里而无所馀。无所馀则领虽设而与不设同矣。家礼既不言其尺度。则其广狭不甚关重。稍广其领于二寸之外。便加二寸之缘而有所馀。亦无妨耶。丘氏二寸为袷。加缘半寸之说似好。而但家礼领缘二寸之说。如彼丁宁。改家礼亦似未安。如何。又窃伏念袷若是别用布为之者。则家礼万无不言尺度之理。礼记虽言袷二寸。而深衣图。皆以加缘者。通谓之曲袷。则所谓曲袷二寸者。未必非领缘二寸。若于两肩上。裁剪后。直以墨缘缀表里二寸。则既不失领缘二寸之数。而其制又不害为方领。如何。
按此乃古人衣服遗制。而于今可以考信者。只有深衣玉藻两篇数段文字。后来诸儒暨朱夫子所论。皆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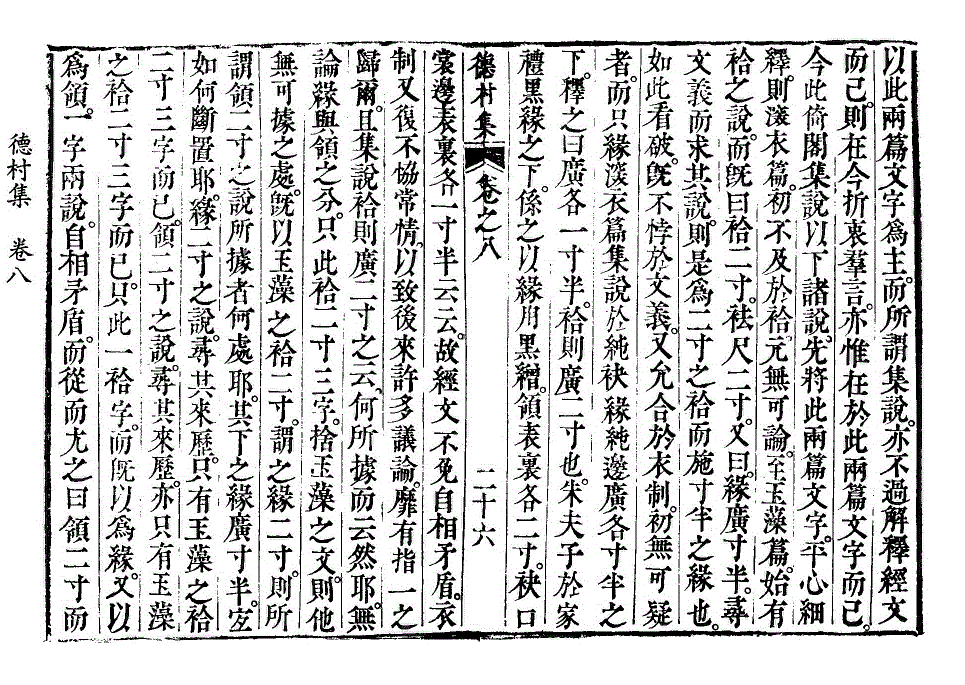 以此两篇文字为主。而所谓集说。亦不过解释经文而已。则在今折衷群言。亦惟在于此两篇文字而已。今此倚阁集说以下诸说。先将此两篇文字。平心细绎。则深衣篇。初不及于袷。元无可论。至玉藻篇。始有袷之说。而既曰袷二寸。袪尺二寸。又曰。缘广寸半。寻文义而求其说。则是为二寸之袷而施寸半之缘也。如此看破。既不悖于文义。又允合于衣制。初无可疑者。而只缘深衣篇集说于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之下。释之曰广各一寸半。袷则广二寸也。朱夫子于家礼黑缘之下。系之以缘用黑缯。领表里各二寸。袂口裳边表里各一寸半云云。故经文不免自相矛盾。衣制又复不协常情。以致后来许多议论。靡有指一之归尔。且集说袷则广二寸之云。何所据而云然耶。无论缘与领之分。只此袷二寸三字。舍玉藻之文。则他无可据之处。既以玉藻之袷二寸。谓之缘二寸。则所谓领二寸之说所据者何处耶。其下之缘广寸半。宜如何断置耶。缘二寸之说。寻其来历。只有玉藻之袷二寸三字而已。领二寸之说。寻其来历。亦只有玉藻之袷二寸三字而已。只此一袷字。而既以为缘。又以为领。一字两说。自相矛盾。而从而尤之曰领二寸而
以此两篇文字为主。而所谓集说。亦不过解释经文而已。则在今折衷群言。亦惟在于此两篇文字而已。今此倚阁集说以下诸说。先将此两篇文字。平心细绎。则深衣篇。初不及于袷。元无可论。至玉藻篇。始有袷之说。而既曰袷二寸。袪尺二寸。又曰。缘广寸半。寻文义而求其说。则是为二寸之袷而施寸半之缘也。如此看破。既不悖于文义。又允合于衣制。初无可疑者。而只缘深衣篇集说于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之下。释之曰广各一寸半。袷则广二寸也。朱夫子于家礼黑缘之下。系之以缘用黑缯。领表里各二寸。袂口裳边表里各一寸半云云。故经文不免自相矛盾。衣制又复不协常情。以致后来许多议论。靡有指一之归尔。且集说袷则广二寸之云。何所据而云然耶。无论缘与领之分。只此袷二寸三字。舍玉藻之文。则他无可据之处。既以玉藻之袷二寸。谓之缘二寸。则所谓领二寸之说所据者何处耶。其下之缘广寸半。宜如何断置耶。缘二寸之说。寻其来历。只有玉藻之袷二寸三字而已。领二寸之说。寻其来历。亦只有玉藻之袷二寸三字而已。只此一袷字。而既以为缘。又以为领。一字两说。自相矛盾。而从而尤之曰领二寸而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59L 页
 缘亦二寸。则袷为虚设矣。实未知其由矣。朱夫子既以领缘二寸。载之家礼。而丘氏于仪节。拟用布阔二寸为袷而加缘寸半于其上。丘氏岂不知改家礼为未安。而以必如此而后。经文方有据依。衣制方为顺轨。故不以为嫌也。第家礼之不言袷尺度。宋龟峰曰。家礼则无袷。只以黑缘二寸。兼袷而用之。盖俭约也。定非阙文也。来谕之云。似与龟峰之说暗合。而但如此则所谓领必待缀缘之广。然后方成如矩之象。与家礼既有方领。又有黑缘之意。不相类。是亦未可知也。大抵家礼深衣之制。如续衽钩边。固是朱夫子未定之论。而此一款。其疏脱又如此。所以备要于方领之下。添入补注一段。于黑缘之下。添入丘氏说一段以补之也。如何。
缘亦二寸。则袷为虚设矣。实未知其由矣。朱夫子既以领缘二寸。载之家礼。而丘氏于仪节。拟用布阔二寸为袷而加缘寸半于其上。丘氏岂不知改家礼为未安。而以必如此而后。经文方有据依。衣制方为顺轨。故不以为嫌也。第家礼之不言袷尺度。宋龟峰曰。家礼则无袷。只以黑缘二寸。兼袷而用之。盖俭约也。定非阙文也。来谕之云。似与龟峰之说暗合。而但如此则所谓领必待缀缘之广。然后方成如矩之象。与家礼既有方领。又有黑缘之意。不相类。是亦未可知也。大抵家礼深衣之制。如续衽钩边。固是朱夫子未定之论。而此一款。其疏脱又如此。所以备要于方领之下。添入补注一段。于黑缘之下。添入丘氏说一段以补之也。如何。问。大带家礼云带用白缯。广四寸。夹缝之。其长围腰而结于前。再缭之为两耳云。疑解以为士之带单二寸。必再缭然后准四寸之数。家礼除再缭而夹缝之云。所谓夹缝者。果是夹作二寸者。则夹缝之下。宜无再缭一节。而既曰夹缝。又曰再缭。若以夹缝作二寸者。再缭腰则是乃单八寸之数。恐无此理。未知此两缭乃为两耳之制。而非玉藻再缭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0H 页
 腰之谓耶。
腰之谓耶。玉藻再缭之文曰。士缁辟二寸。再缭四寸云。则不待注说而可知其为再缭腰矣。家礼再缭之文。不曰再缭而结于前。而曰围腰而结于前。再缭之为两耳云。则所谓再缭。乃为两耳之制。而非再缭腰之谓也。字虽同而制则殊。无可疑者。然王(一作玉)藻之再缭。其围腰处虽准四寸之数。而馀垂者依然是二寸之带。是未可晓也。
问。家礼每位陈设图。脯醢蔬菜。各用三器。一色三器。未知何义。且家礼备要。皆果用六色。而要诀用五色。亦未知何义。
一色三器之疑。诚如来谕。然无亦以脯醢非一种。蔬菜亦非一种。非如饭羹面饼等之有定名。故通称脯醢蔬菜。列书于六行。而随其时各品之意。自在其中。如果非一色。而列书一果字于六行耶。其涤器具馔下注曰。蔬菜及脯醢各三品。可见其三器之非一色矣。家礼之馔品色数。盖寓天地奇偶之意。而要诀之果五色。未知别有何意。未敢容喙。
问。丧礼备要初卷立丧主小注。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云者。未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0L 页
 知何谓。
知何谓。礼记丧服小记集说。大煞分明。有何可疑乎。其小注金华应氏说。尤为详备。更加考阅。
问。易服条男子扱上衽注。扱深衣前襟于带云。扱字乃插字也。谓其不系小带而插前襟于大带耶。今人例于被发后。即袒上衣。以其所袒之襟。插于小带。此其习谬而然耶。至饭含条。始言袒。则易服时不袒可知。如何。
按闻丧篇集说曰。上衽。深衣前襟也。以号踊践履为妨教。扱之于带也。虽不分小带与大带。而至去华饰条仪节。以为华饰。谓衣服之有色者。男子腰带。妇人首饰云。则深衣之大带仍带未安。今人之插之于小带。亦或以此也耶。易服时不袒云云。来谕恐得之矣。
问。家礼小敛条。遂小敛下注曰。又卷衣夹其两胫。取其方正然后以馀衣掩尸。左衽不纽云。备要小敛条注曰。按家礼左衽不纽。与丧大记结绞不纽不同云。其下又曰。丧大记初不言袭。而仪礼及家礼。亦无袭时左衽之说。郑注恐不可从云。然则所谓馀衣。乃袭馀之衣而不著于尸体者。不著之衣。何论衽之左右。且既左衽则自无可系之带。又何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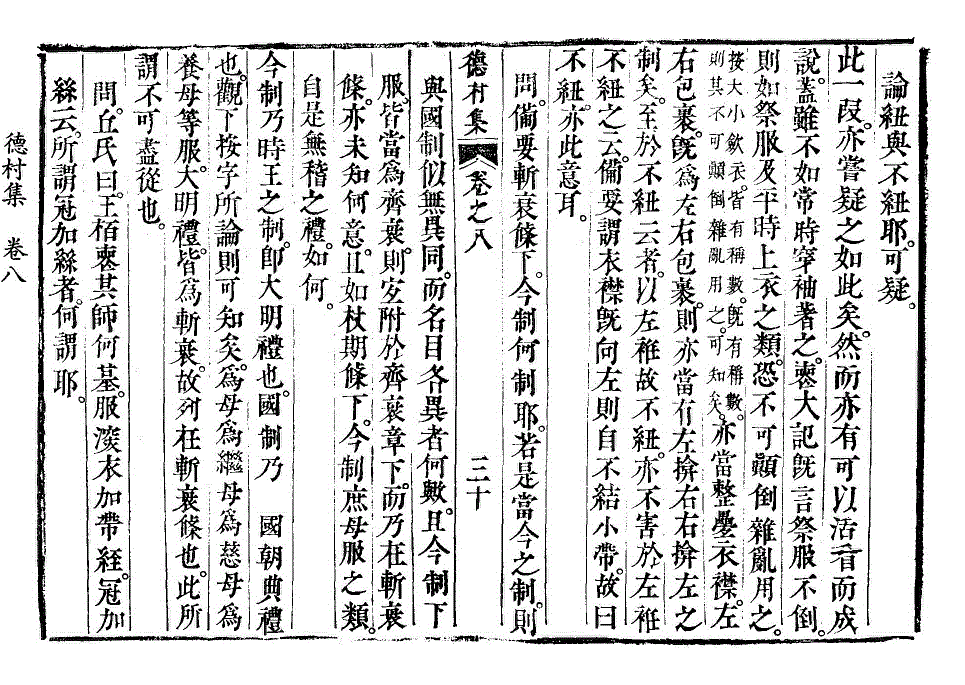 论纽与不纽耶。可疑。
论纽与不纽耶。可疑。此一段。亦尝疑之如此矣。然而亦有可以活看而成说。盖虽不如常时穿袖著之。丧大记既言祭服不倒。则如祭服及平时上衣之类。恐不可颠倒杂乱用之。(按大小敛衣。皆有称数。既有称数。则其不可颠倒杂乱用之。可知矣。)亦当整叠衣襟。左右包裹。既为左右包裹。则亦当有左掩右右掩左之制矣。至于不纽云者。以左衽故不纽。亦不害于左衽不纽之云。备要谓衣襟既向左则自不结小带。故曰不纽。亦此意耳。
问。备要斩衰条下。今制何制耶。若是当今之制。则与国制似无异同。而名目各异者何欤。且今制下服。皆当为齐衰。则宜附于齐衰章下。而乃在斩衰条。亦未知何意。且如杖期条下。今制庶母服之类。自是无稽之礼。如何。
今制乃时王之制。即大明礼也。国制乃 国朝典礼也。观下按字所论则可知矣。为母为继母为慈母为养母等服。大明礼。皆为斩衰。故列在斩衰条也。此所谓不可尽从也。
问。丘氏曰。王柏丧其师何基。服深衣加带绖。冠加丝云。所谓冠加丝者。何谓耶。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1L 页
 所谓冠加丝武者。恐是以丝为冠之武也。
所谓冠加丝武者。恐是以丝为冠之武也。问。祔祭祝。仪礼则曰孝子某适尔皇祖某甫。以隮祔尔孙某甫。家礼则曰孝子某适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孙某官云。丧礼备要则曰孤子某适于显曾祖考某官府君。隮祔孙某官云。凡丧。卒哭后用祭礼。故仪礼家礼皆用孝子。则备要之改以孤子。何意耶。尔祖之称。不可用于今。某考之称。亦似未莹。果不如直称以曾祖之为分明。而但祝文既称以曾祖考。则卒哭祝下祔祭告辞。亦当曰来日隮祔于曾祖考而曰祖考。此其意虽谓亡者之祖考。而以主丧者称以祖考。殊未莹。且曾祖之前。自称孝子孤子者亦未安。如何。
果不如备要直称曾祖考之为分明。诚如来谕。而孝字之改以孤字。实未知其故矣。其不曰隮祔于曾祖考而曰隮祔于祖考。恐是以隮祔为主。而据昭穆为称故云然耶。曾祖之前。自称孝子。退溪答郑寒冈曰。家礼岂不以此祭主于升祔先考先妣而设。故只称孝子耶。
问。时祭卜日条。主人搢笏焚香薰珓。而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将以来月某日。诹此岁事。适其祖考云。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2H 页
 诹字未知何意。适字。即祔祭适于祖考之适字。则恐是主字之意。如何。
诹字未知何意。适字。即祔祭适于祖考之适字。则恐是主字之意。如何。诹字之义。以卜其吉凶之意推之。则恐是问字之意。适其祖考之适字。即祔祭适于祖考之适字。而此字之意。寻常未解。来示主字之意。亦未知其必为稳当。须得古注之端的训义。然后方可据守矣。如何。
问。家礼时祭条陈器下注。朱子曰。考诸程先生之言。则高祖有服。不可不祭。虽七庙五庙。亦止于高祖。三庙一庙。以至祭寝。亦必及于高祖云。所谓七庙五庙。亦止高祖云者何谓耶。谓其虽为七庙五庙。而祭则止于高祖耶。三庙一庙。以至祭寝云者。亦未知何谓。
礼记丧服小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集说曰。四庙谓高曾祖祢四亲庙也。始祖居中为五。并高祖之父祖为七庙。小注严陵方氏曰。王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此言王者。止立四庙者。据月祭之亲庙言也。○祭法曰。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集说曰。考庙父庙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显考高祖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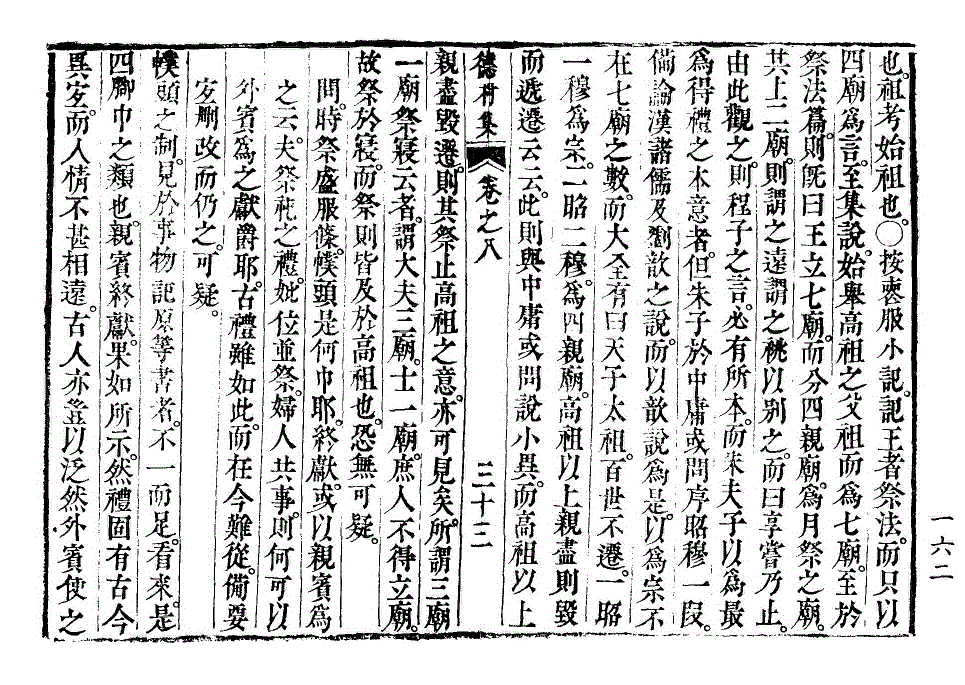 也。祖考始祖也。○按丧服小记。记王者祭法。而只以四庙为言。至集说。始举高祖之父祖而为七庙。至于祭法篇。则既曰王立七庙。而分四亲庙。为月祭之庙。其上二庙。则谓之远谓之祧以别之。而曰享尝乃止。由此观之。则程子之言。必有所本。而朱夫子以为最为得礼之本意者。但朱子于中庸或问序昭穆一段。备论汉诸儒及刘歆之说。而以歆说为是。以为宗不在七庙之数。而大全有曰天子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为宗。二昭二穆。为四亲庙。高祖以上亲尽则毁而递迁云云。此则与中庸或问说小异。而高祖以上亲尽毁迁。则其祭止高祖之意。亦可见矣。所谓三庙一庙祭寝云者。谓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得立庙。故祭于寝。而祭则皆及于高祖也。恐无可疑。
也。祖考始祖也。○按丧服小记。记王者祭法。而只以四庙为言。至集说。始举高祖之父祖而为七庙。至于祭法篇。则既曰王立七庙。而分四亲庙。为月祭之庙。其上二庙。则谓之远谓之祧以别之。而曰享尝乃止。由此观之。则程子之言。必有所本。而朱夫子以为最为得礼之本意者。但朱子于中庸或问序昭穆一段。备论汉诸儒及刘歆之说。而以歆说为是。以为宗不在七庙之数。而大全有曰天子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为宗。二昭二穆。为四亲庙。高祖以上亲尽则毁而递迁云云。此则与中庸或问说小异。而高祖以上亲尽毁迁。则其祭止高祖之意。亦可见矣。所谓三庙一庙祭寝云者。谓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得立庙。故祭于寝。而祭则皆及于高祖也。恐无可疑。问。时祭盛服条。幞头是何巾耶。终献。或以亲宾为之云。夫祭祀之礼。妣位并祭。妇人共事。则何可以外宾为之献爵耶。古礼虽如此。而在今难从。备要宜删改而仍之。可疑。
幞头之制。见于事物记原等书者。不一而足。看来。是四脚巾之类也。亲宾终献。果如所示。然礼固有古今异宜。而人情不甚相远。古人亦岂以泛然外宾使之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3H 页
 献爵耶。在今虽是不常有之事。而直为删去。恐似未安。如何。
献爵耶。在今虽是不常有之事。而直为删去。恐似未安。如何。问。无后死者之妻。立后于三年之内。其所后子既制三年之服。则服制未尽而丧期先尽。此其撤几筵一节。何以为之。臆见有可以旁照者。盖为人后追服之节。当如闻丧晚。追服之礼。此则有明文。闻丧晚者。若为宗子。则虽其闻丧在经年之后。亦当以所闻之日为始。以终三年之制而后撤几筵也。追为后者。仍存几筵于再期之后。亦何不可。况祥禫之祭。所后子当主之。再期日。虽略设祭奠。而此则非祥祭也。未祥之前。先撤几筵。尤未妥当。如何。
来示所谓闻丧晚。追服之节。可以旁照云者。恐得制礼者之微旨矣。问解练后。为后者税服一段。以司马操之言为是。司马操之言。虽不言几筵之撤否。而其所谓父子之名。定于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于辞亲之日及彼丧虽杀。我重自始等诸说。大义昭然。无可疑者。几筵一节。恐亦自在其中矣。
答李端徽书(甲辰)
邂逅一面之后。苦未有承晤之便。一心驰仰。时自憧憧。忽此承翰。谨审酷炎。启处神相。殊切喜幸。示意谨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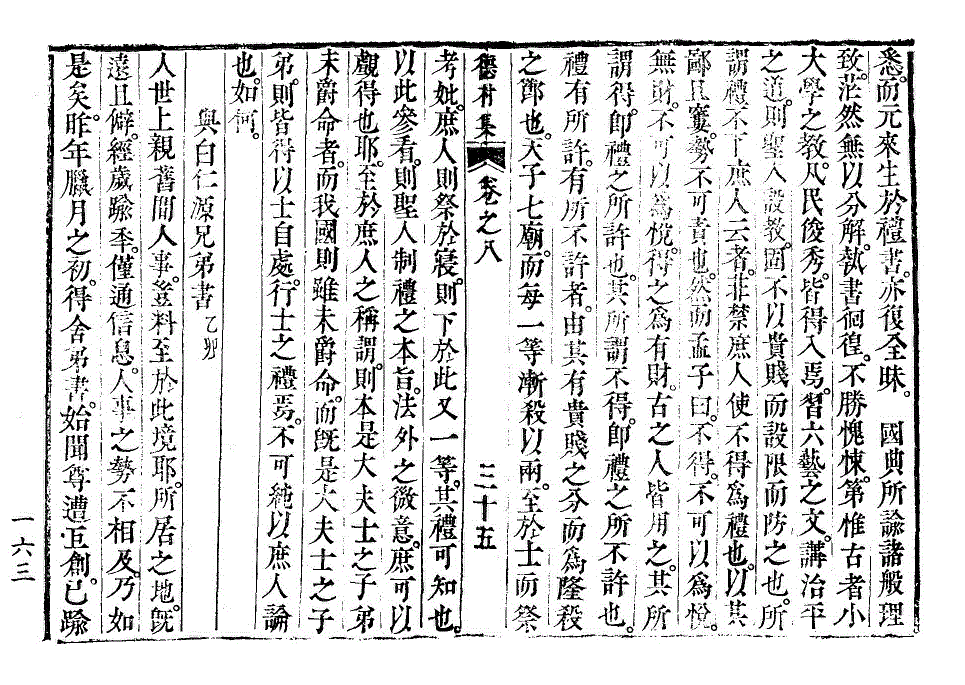 悉。而元来生于礼书。亦复全昧。 国典所谕诸般理致。茫然无以分解。执书徊徨。不胜愧悚。第惟古者小大学之教。凡民俊秀。皆得入焉。习六艺之文。讲治平之道。则圣人设教。固不以贵贱而设限而防之也。所谓礼不下庶人云者。非禁庶人使不得为礼也。以其鄙且窭。势不可责也。然而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其所谓得。即礼之所许也。其所谓不得。即礼之所不许也。礼有所许。有所不许者。由其有贵贱之分而为隆杀之节也。天子七庙。而每一等渐杀以两。至于士而祭考妣。庶人则祭于寝。则下于此又一等。其礼可知也。以此参看。则圣人制礼之本旨。法外之微意。庶可以觑得也耶。至于庶人之称谓。则本是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而我国则虽未爵命。而既是大夫士之子弟。则皆得以士自处。行士之礼焉。不可纯以庶人论也。如何。
悉。而元来生于礼书。亦复全昧。 国典所谕诸般理致。茫然无以分解。执书徊徨。不胜愧悚。第惟古者小大学之教。凡民俊秀。皆得入焉。习六艺之文。讲治平之道。则圣人设教。固不以贵贱而设限而防之也。所谓礼不下庶人云者。非禁庶人使不得为礼也。以其鄙且窭。势不可责也。然而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其所谓得。即礼之所许也。其所谓不得。即礼之所不许也。礼有所许。有所不许者。由其有贵贱之分而为隆杀之节也。天子七庙。而每一等渐杀以两。至于士而祭考妣。庶人则祭于寝。则下于此又一等。其礼可知也。以此参看。则圣人制礼之本旨。法外之微意。庶可以觑得也耶。至于庶人之称谓。则本是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而我国则虽未爵命。而既是大夫士之子弟。则皆得以士自处。行士之礼焉。不可纯以庶人论也。如何。与白仁源兄弟书(乙卯)
人世上亲旧间人事。岂料至于此境耶。所居之地。既远且僻。经岁踰年。仅通信息。人事之势不相及。乃如是矣。昨年腊月之初。得舍弟书。始闻尊遭巨创。已踰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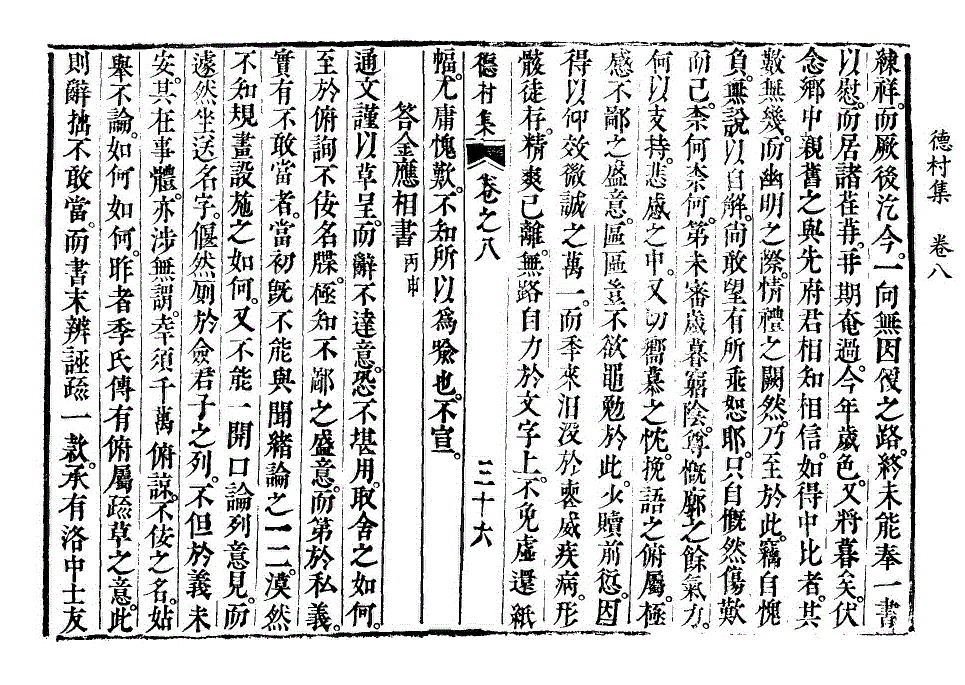 练祥。而厥后汔今。一向无因便之路。终未能奉一书以慰。而居诸荏苒。再期奄过。今年岁色。又将暮矣。伏念乡中亲旧之与先府君相知相信。如得中比者。其数无几。而幽明之际。情礼之阙然。乃至于此。窃自愧负。无说以自解。尚敢望有所垂恕耶。只自慨然伤叹而已。柰何柰何。第未审岁暮穷阴。尊慨廓之馀气力。何以支持。悲感之中。又切向慕之忱。挽语之俯属。极感不鄙之盛意。区区岂不欲黾勉于此。少赎前愆。因得以仰效微诚之万一。而年来汩没于丧威疾病。形骸徒存。精爽已离。无路自力于文字上。不免虚还纸幅。尤庸愧叹。不知所以为喻也。不宣。
练祥。而厥后汔今。一向无因便之路。终未能奉一书以慰。而居诸荏苒。再期奄过。今年岁色。又将暮矣。伏念乡中亲旧之与先府君相知相信。如得中比者。其数无几。而幽明之际。情礼之阙然。乃至于此。窃自愧负。无说以自解。尚敢望有所垂恕耶。只自慨然伤叹而已。柰何柰何。第未审岁暮穷阴。尊慨廓之馀气力。何以支持。悲感之中。又切向慕之忱。挽语之俯属。极感不鄙之盛意。区区岂不欲黾勉于此。少赎前愆。因得以仰效微诚之万一。而年来汩没于丧威疾病。形骸徒存。精爽已离。无路自力于文字上。不免虚还纸幅。尤庸愧叹。不知所以为喻也。不宣。答金应相书(丙申)
通文谨以草呈。而辞不达意。恐不堪用。取舍之如何。至于俯询不佞名牒。极知不鄙之盛意。而第于私义。实有不敢当者。当初既不能与闻绪论之一二。漠然不知规画设施之如何。又不能一开口论列意见。而遽然坐送名字。偃然厕于佥君子之列。不但于义未安。其在事体。亦涉无谓。幸须千万俯谅。不佞之名。姑举不论。如何如何。昨者季氏传有俯属疏草之意。此则辞拙不敢当。而书末辨诬疏一款。承有洛中士友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4L 页
 云云。大抵此等事。苟于义理当为。则便当为之。而其谓之当为之人。便当自为之。不合更劝别人。从前每见京里若有人主张此论。而亦不自为之。而欲使此中人奔走奉行者然。迂愚之见。实未知其故。然崔洗马之疏已上矣。此后一著。似当更看向后节拍然后徐以应之。姑勿纷纭。乃鄙之所深祈者也。如何如何。
云云。大抵此等事。苟于义理当为。则便当为之。而其谓之当为之人。便当自为之。不合更劝别人。从前每见京里若有人主张此论。而亦不自为之。而欲使此中人奔走奉行者然。迂愚之见。实未知其故。然崔洗马之疏已上矣。此后一著。似当更看向后节拍然后徐以应之。姑勿纷纭。乃鄙之所深祈者也。如何如何。答李寿而(颐期书。丙申。寿而为疏事留京。书问京人议。示之以毁誉二字故答之。)
春初奉别。忽忽如梦里事。意外承拜宠翰。醒然如更接清晤。况审此时旅况珍重。尤用慰豁。弟二月念后。还到茅亭。见过祥事。去月之初。得达陋栖耳。师门辨诬。大明中天。群妖屏迹。不惟使一时阴邪破胆慄魄。直将从来大是非定。作万古不易之断案。盖阴之不能胜阳。邪之不能胜正。终归于天定而不容已也。小人之假真售伪于一时者。亦可以知所惧矣。缕缕见谕。仰感盛意。而窃叹夫左右者之不深惟事理之归趣。而猥随俗之毁誉也。夫所谓无辨云者。岂固无辨而已哉。诚以强聒不可入之言。以益其譊譊。不如默焉而自修。以守其不可没之实。则始虽世短于一时。而终无柰道长于千载也。今虽无大君子大力量。不免落于第二义。而亦岂容随人对掌。随语对辨。以自
德村先生集卷之八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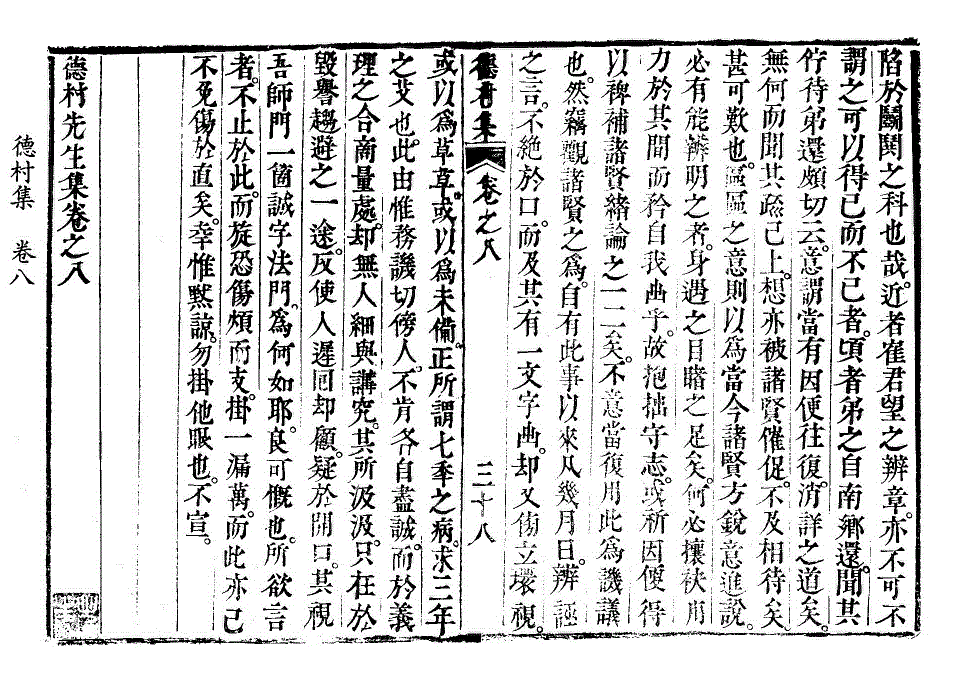 陷于斗鬨之科也哉。近者崔君望之辨章。亦不可不谓之可以得已而不已者。顷者弟之自南乡还。闻其伫待弟还颇切云。意谓当有因便往复。消详之道矣。无何而闻其疏已上。想亦被诸贤催促。不及相待矣。甚可叹也。区区之意则以为当今诸贤方锐意进说。必有能辨明之者。身遇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于其间而矜自我出乎。故抱拙守志。或祈因便得以裨补诸贤绪论之一二矣。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然窃观诸贤之为。自有此事以来凡几月日。辨诬之言。不绝于口。而及其有一文字出。却又傍立𡑡视。或以为草草。或以为未备。正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此由惟务讥切傍人。不肯各自尽诚。而于义理之合商量处。却无人细与讲究。其所汲汲。只在于毁誉趋避之一途。反使人迟回却顾。疑于开口。其视吾师门一个诚字法门。为何如耶。良可慨也。所欲言者。不止于此。而旋恐伤烦而支。挂一漏万。而此亦已不免伤于直矣。幸惟默谅。勿挂他眼也。不宣。
陷于斗鬨之科也哉。近者崔君望之辨章。亦不可不谓之可以得已而不已者。顷者弟之自南乡还。闻其伫待弟还颇切云。意谓当有因便往复。消详之道矣。无何而闻其疏已上。想亦被诸贤催促。不及相待矣。甚可叹也。区区之意则以为当今诸贤方锐意进说。必有能辨明之者。身遇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于其间而矜自我出乎。故抱拙守志。或祈因便得以裨补诸贤绪论之一二矣。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然窃观诸贤之为。自有此事以来凡几月日。辨诬之言。不绝于口。而及其有一文字出。却又傍立𡑡视。或以为草草。或以为未备。正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此由惟务讥切傍人。不肯各自尽诚。而于义理之合商量处。却无人细与讲究。其所汲汲。只在于毁誉趋避之一途。反使人迟回却顾。疑于开口。其视吾师门一个诚字法门。为何如耶。良可慨也。所欲言者。不止于此。而旋恐伤烦而支。挂一漏万。而此亦已不免伤于直矣。幸惟默谅。勿挂他眼也。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