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明美堂集卷十 第 x 页
明美堂集卷十(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序
序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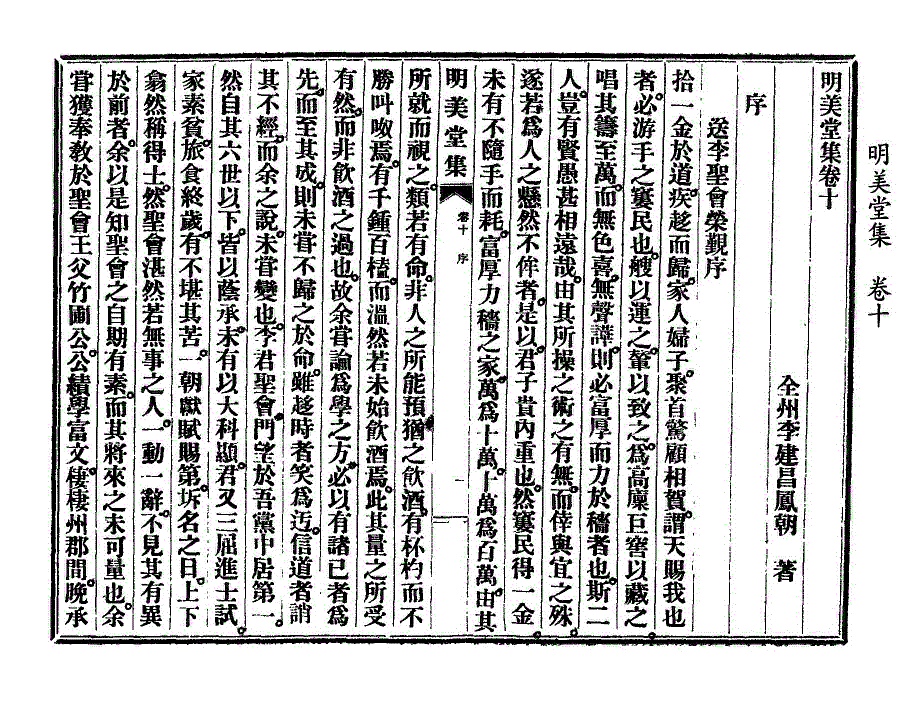 送李圣会荣觐序
送李圣会荣觐序拾一金于道。疾趍而归。家人妇子。聚首惊顾相贺。谓天赐我也者。必游手之窭民也。艘以运之。辇以致之。为高廪巨窖以藏之。唱其筹至万。而无色喜。无声哗。则必富厚而力于穑者也。斯二人。岂有贤愚甚相远哉。由其所操之术之有无。而倖与宜之殊。遂若为人之悬然不侔者。是以。君子贵内重也。然窭民得一金。未有不随手而耗。富厚力穑之家。万为十万。十万为百万。由其所就而视之。类若有命。非人之所能预。犹之饮酒。有杯杓而不胜叫呶焉。有千钟百榼。而温然若未始饮酒焉。此其量之所受有然。而非饮酒之过也。故余尝论为学之方。必以有诸己者为先。而至其成。则未尝不归之于命。虽趍时者笑为迂。信道者诮其不经。而余之说。未尝变也。李君圣会。门望于吾党中居第一。然自其六世以下。皆以荫承。未有以大科显。君又三屈进士试。家素贫。旅食终岁。有不堪其苦。一朝献赋赐第。坼名之日。上下翕然称得士。然圣会湛然若无事之人。一动一辞。不见其有异于前者。余以是知圣会之自期有素。而其将来之未可量也。余尝获奉教于圣会王父竹圃公。公绩学富文。栖栖州郡间。晚承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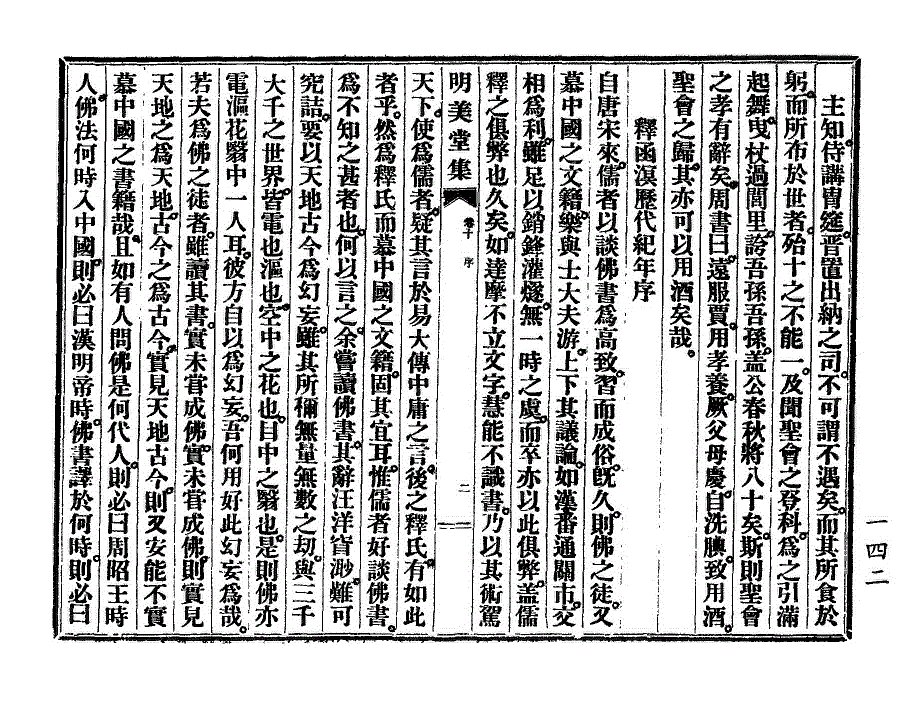 主知。侍讲胄筵。晋置出纳之司。不可谓不遇矣。而其所食于躬。而所布于世者。殆十之不能一。及闻圣会之登科。为之引满起舞。曳杖过闾里。誇吾孙吾孙。盖公春秋将八十矣。斯则圣会之孝有辞矣。周书曰。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圣会之归。其亦可以用酒矣哉。
主知。侍讲胄筵。晋置出纳之司。不可谓不遇矣。而其所食于躬。而所布于世者。殆十之不能一。及闻圣会之登科。为之引满起舞。曳杖过闾里。誇吾孙吾孙。盖公春秋将八十矣。斯则圣会之孝有辞矣。周书曰。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圣会之归。其亦可以用酒矣哉。释函溟历代纪年序
自唐宋来。儒者以谈佛书为高致。习而成俗。既久。则佛之徒。又慕中国之文籍。乐与士大夫游。上下其议论。如汉,番通关市。交相为利。虽足以销锋灌燧。无一时之虞。而卒亦以此俱弊。盖儒释之俱弊也久矣。如达摩不立文字。慧能不识书。乃以其术驾天下。使为儒者。疑其言于易大传中庸之言。后之释氏。有如此者乎。然为释氏而慕中国之文籍。固其宜耳。惟儒者好谈佛书。为不知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余尝读佛书。其辞汪洋窅渺。难可究诘。要以天地古今为幻妄。虽其所称无量无数之劫。与三千大千之世界。皆电也沤也。空中之花也。目中之翳也。是则佛亦电沤花翳中一人耳。彼方自以为幻妄。吾何用好此幻妄为哉。若夫为佛之徒者。虽读其书。实未尝成佛。实未尝成佛。则实见天地之为天地。古今之为古今。实见天地古今。则又安能不实慕中国之书籍哉。且如有人问佛是何代人。则必曰周昭王时人。佛法何时入中国。则必曰汉明帝时。佛书译于何时。则必曰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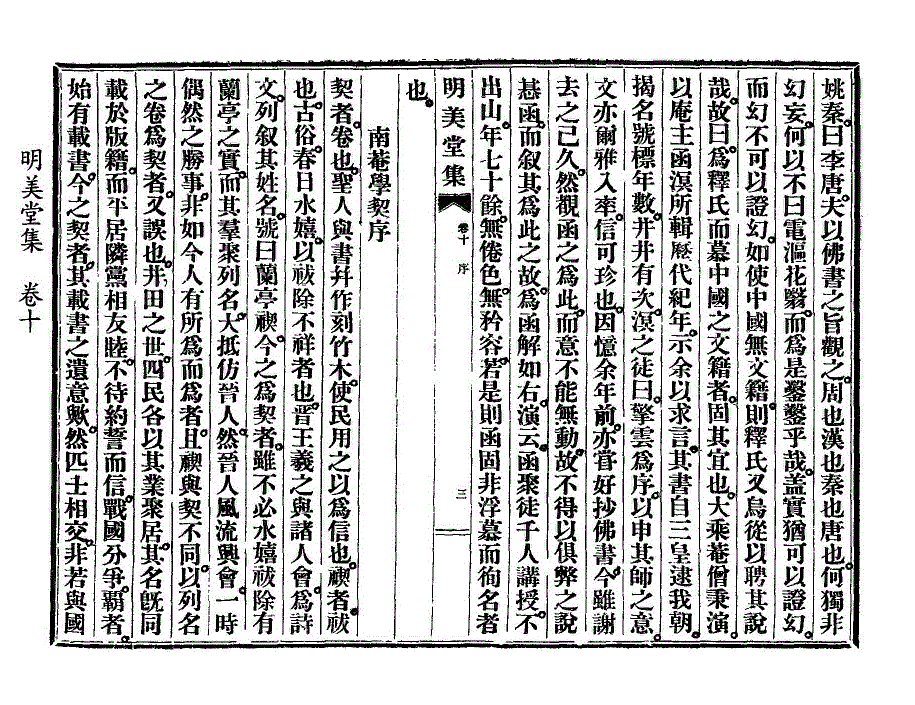 姚秦。曰李唐。夫以佛书之旨观之。周也汉也秦也唐也。何独非幻妄。何以不曰电沤花翳。而为是凿凿乎哉。盖实犹可以證幻。而幻不可以證幻。如使中国无文籍。则释氏又乌从以聘其说哉。故曰。为释氏而慕中国之文籍者。固其宜也。大乘庵僧秉演。以庵主函溟所辑历代纪年。示余以求言。其书自三皇逮我朝。揭名号标年数。井井有次。溟之徒曰。擎云为序。以申其师之意。文亦尔雅入率。信可珍也。因忆余年前。亦尝好抄佛书。今虽谢去之已久。然睹函之为此。而意不能无动。故不得以俱弊之说惎函。而叙其为此之故。为函解如右。演云。函聚徒千人讲授。不出山。年七十馀。无倦色。无矜容。若是则函固非浮慕而徇名者也。
姚秦。曰李唐。夫以佛书之旨观之。周也汉也秦也唐也。何独非幻妄。何以不曰电沤花翳。而为是凿凿乎哉。盖实犹可以證幻。而幻不可以證幻。如使中国无文籍。则释氏又乌从以聘其说哉。故曰。为释氏而慕中国之文籍者。固其宜也。大乘庵僧秉演。以庵主函溟所辑历代纪年。示余以求言。其书自三皇逮我朝。揭名号标年数。井井有次。溟之徒曰。擎云为序。以申其师之意。文亦尔雅入率。信可珍也。因忆余年前。亦尝好抄佛书。今虽谢去之已久。然睹函之为此。而意不能无动。故不得以俱弊之说惎函。而叙其为此之故。为函解如右。演云。函聚徒千人讲授。不出山。年七十馀。无倦色。无矜容。若是则函固非浮慕而徇名者也。南庵学契序
契者。卷也。圣人与书并作刻竹木。使民用之以为信也。禊者。祓也。古俗。春日水嬉。以祓除不祥者也。晋王羲之与诸人会。为诗文。列叙其姓名。号曰兰亭禊。今之为契者。虽不必水嬉祓除有兰亭之实。而其群聚列名。大抵仿晋人。然晋人风流兴会。一时偶然之胜事。非如今人有所为而为者。且禊与契不同。以列名之卷为契者。又误也。井田之世。四民各以其业聚居。其名既同载于版籍。而平居邻党相友睦。不待约誓而信。战国分争。霸者。始有载书。今之契者。其载书之遗意欤。然匹士相交。非若与国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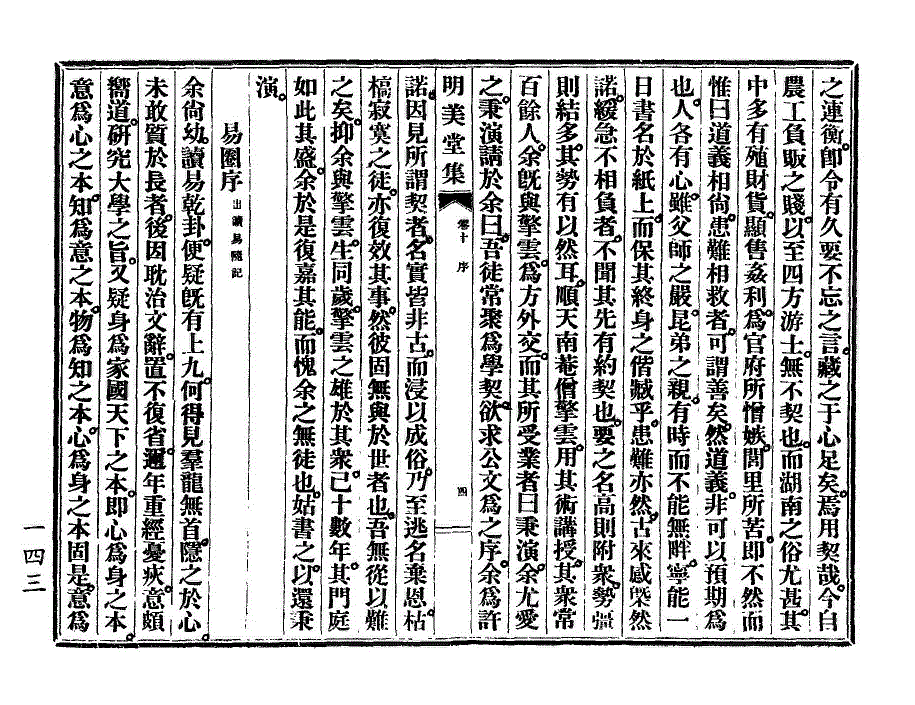 之连衡。即令有久要不忘之言。藏之于心足矣。焉用契哉。今自农工负贩之贱。以至四方游士。无不契也。而湖南之俗尤甚。其中多有殖财货。显售奸利。为官府所憎嫉。闾里所苦。即不然而惟曰道义相尚。患难相救者。可谓善矣。然道义。非可以预期为也。人各有心。虽父师之严。昆弟之亲。有时而不能无畔。宁能一日书名于纸上。而保其终身之偕臧乎。患难亦然。古来感槩然诺。缓急不相负者。不闻其先有约契也。要之名高则附众。势彊则结多。其势有以然耳。顺天南庵僧擎云。用其术讲授。其众常百馀人。余既与擎云。为方外交。而其所受业者曰秉演。余尤爱之。秉演请于余曰。吾徒常聚为学契。欲求公文为之序。余为许诺。因见所谓契者。名实皆非古。而浸以成俗。乃至逃名弃恩。枯槁寂寞之徒。亦复效其事。然彼固无与于世者也。吾无从以难之矣。抑余与擎云。生同岁。擎云之雄于其众。已十数年。其门庭如此其盛。余于是复嘉其能。而愧余之无徒也。姑书之。以还秉演。
之连衡。即令有久要不忘之言。藏之于心足矣。焉用契哉。今自农工负贩之贱。以至四方游士。无不契也。而湖南之俗尤甚。其中多有殖财货。显售奸利。为官府所憎嫉。闾里所苦。即不然而惟曰道义相尚。患难相救者。可谓善矣。然道义。非可以预期为也。人各有心。虽父师之严。昆弟之亲。有时而不能无畔。宁能一日书名于纸上。而保其终身之偕臧乎。患难亦然。古来感槩然诺。缓急不相负者。不闻其先有约契也。要之名高则附众。势彊则结多。其势有以然耳。顺天南庵僧擎云。用其术讲授。其众常百馀人。余既与擎云。为方外交。而其所受业者曰秉演。余尤爱之。秉演请于余曰。吾徒常聚为学契。欲求公文为之序。余为许诺。因见所谓契者。名实皆非古。而浸以成俗。乃至逃名弃恩。枯槁寂寞之徒。亦复效其事。然彼固无与于世者也。吾无从以难之矣。抑余与擎云。生同岁。擎云之雄于其众。已十数年。其门庭如此其盛。余于是复嘉其能。而愧余之无徒也。姑书之。以还秉演。易圈序(出读易随记)
余尚幼。读易乾卦。便疑既有上九。何得见群龙无首。隐之于心。未敢质于长者。后因耽治文辞。置不复省。迩年重经忧疢。意颇向道。研究大学之旨。又疑身为家国天下之本。即心为身之本。意为心之本。知为意之本。物为知之本。心为身之本固是。意为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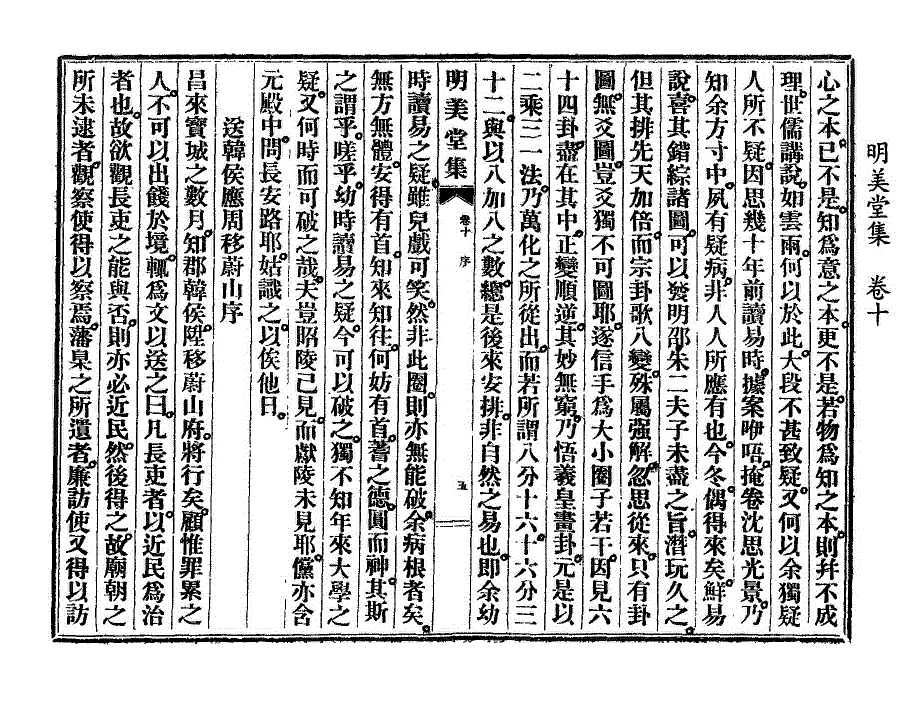 心之本。已不是。知为意之本。更不是。若物为知之本。则并不成理。世儒讲说。如云雨。何以于此。大段不甚致疑。又何以余独疑人所不疑。因思几十年前读易时。据案咿唔。掩卷沈思光景。乃知余方寸中。夙有疑病。非人人所应有也。今冬。偶得来矣。鲜易说。喜其错综诸图。可以发明邵,朱二夫子未尽之旨。潜玩久之。但其排先天加倍。而宗卦歌八变。殊属强解。忽思从来。只有卦图。无爻图。岂爻独不可图耶。遂信手为大小圈子若干。因见六十四卦。尽在其中。正变顺逆。其妙无穷。乃悟羲皇画卦。元是以二乘三一法。乃万化之所从出。而若所谓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与以八加八之数。总是后来安排。非自然之易也。即余幼时读易之疑。虽儿戏可笑。然非此圈。则亦无能破。余病根者矣。无方无体。安得有首。知来知往。何妨有首。蓍之德。圆而神。其斯之谓乎。嗟乎。幼时读易之疑。今可以破之。独不知年来大学之疑。又何时而可破之哉。夫岂昭陵已见。而献陵未见耶。傥亦含元殿中。问长安路耶。姑识之。以俟他日。
心之本。已不是。知为意之本。更不是。若物为知之本。则并不成理。世儒讲说。如云雨。何以于此。大段不甚致疑。又何以余独疑人所不疑。因思几十年前读易时。据案咿唔。掩卷沈思光景。乃知余方寸中。夙有疑病。非人人所应有也。今冬。偶得来矣。鲜易说。喜其错综诸图。可以发明邵,朱二夫子未尽之旨。潜玩久之。但其排先天加倍。而宗卦歌八变。殊属强解。忽思从来。只有卦图。无爻图。岂爻独不可图耶。遂信手为大小圈子若干。因见六十四卦。尽在其中。正变顺逆。其妙无穷。乃悟羲皇画卦。元是以二乘三一法。乃万化之所从出。而若所谓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与以八加八之数。总是后来安排。非自然之易也。即余幼时读易之疑。虽儿戏可笑。然非此圈。则亦无能破。余病根者矣。无方无体。安得有首。知来知往。何妨有首。蓍之德。圆而神。其斯之谓乎。嗟乎。幼时读易之疑。今可以破之。独不知年来大学之疑。又何时而可破之哉。夫岂昭陵已见。而献陵未见耶。傥亦含元殿中。问长安路耶。姑识之。以俟他日。送韩侯应周移蔚山序
昌来宝城之数月。知郡韩侯。升移蔚山府。将行矣。顾惟罪累之人。不可以出饯于境。辄为文以送之曰。凡长吏者。以近民为治者也。故欲观长吏之能与否。则亦必近民。然后得之。故庙朝之所未逮者。观察使得以察焉。藩臬之所遗者。廉访使又得以访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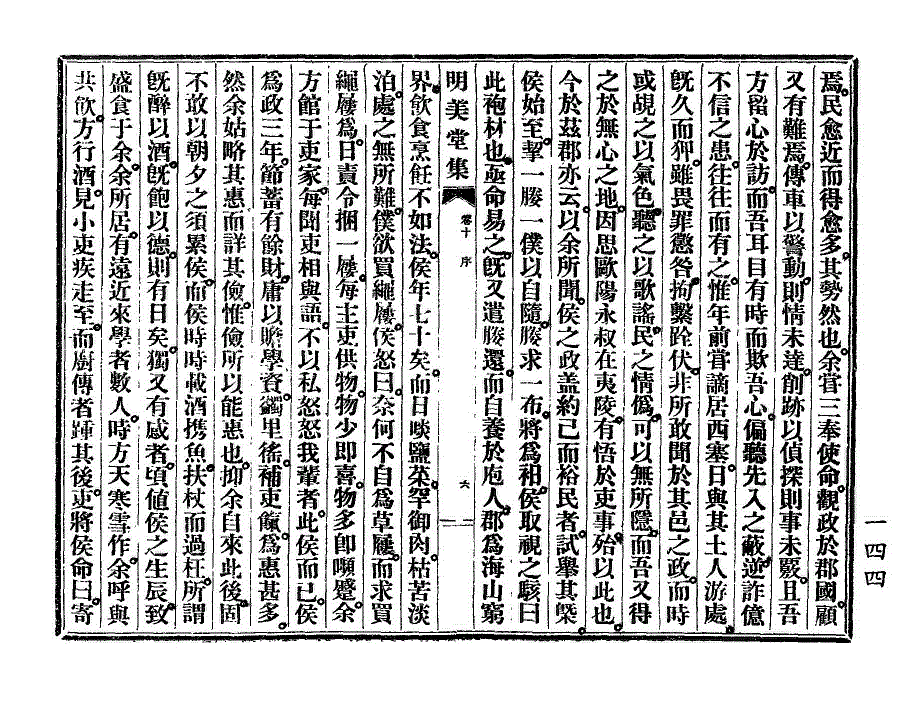 焉。民愈近而得愈多。其势然也。余尝三奉使命。观政于郡国。顾又有难焉。传车以警动。则情未达。削迹以侦探则事未覈。且吾方留心于访。而吾耳目有时而欺吾心。偏听先入之蔽。逆诈亿不信之患。往往而有之。惟年前尝谪居西塞。日与其土人游处。既久而狎。虽畏罪惩咎。拘系跧伏。非所敢闻于其邑之政。而时或觇之以气色。听之以歌谣。民之情伪。可以无所隐。而吾又得之于无心之地。因思欧阳永叔在夷陵。有悟于吏事。殆以此也。今于兹郡亦云。以余所闻。侯之政盖约己而裕民者。试举其槩。侯始至。挈一媵一仆以自随。媵求一布。将为衵。侯取视之骇曰此袍材也。亟命易之。既又遣媵还。而自养于庖人。郡为海山穷界。饮食烹饪不如法。侯年七十矣。而日啖盐菜。罕御肉。枯苦淡泊。处之无所难。仆欲买绳屦。侯怒曰。奈何不自为草屦。而求买绳屦为。日责令捆一屦。每主吏供物。物少即喜。物多即嚬蹙。余方馆于吏家。每闻吏相与语。不以私怒怒我辈者。此侯而已。侯为政三年。节蓄有馀财。庸以赡学资。蠲里徭。补吏饩。为惠甚多。然余姑略其惠而详其俭。惟俭所以能惠也。抑余自来此后。固不敢以朝夕之须累侯。而侯时时载酒携鱼。扶杖而过枉。所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则有日矣。独又有感者。顷值侯之生辰。致盛食于余。余所居。有远近来学者数人。时方天寒雪作。余呼与共饮。方行酒。见小吏疾走至。而厨传者踵其后。吏将侯命曰。寄
焉。民愈近而得愈多。其势然也。余尝三奉使命。观政于郡国。顾又有难焉。传车以警动。则情未达。削迹以侦探则事未覈。且吾方留心于访。而吾耳目有时而欺吾心。偏听先入之蔽。逆诈亿不信之患。往往而有之。惟年前尝谪居西塞。日与其土人游处。既久而狎。虽畏罪惩咎。拘系跧伏。非所敢闻于其邑之政。而时或觇之以气色。听之以歌谣。民之情伪。可以无所隐。而吾又得之于无心之地。因思欧阳永叔在夷陵。有悟于吏事。殆以此也。今于兹郡亦云。以余所闻。侯之政盖约己而裕民者。试举其槩。侯始至。挈一媵一仆以自随。媵求一布。将为衵。侯取视之骇曰此袍材也。亟命易之。既又遣媵还。而自养于庖人。郡为海山穷界。饮食烹饪不如法。侯年七十矣。而日啖盐菜。罕御肉。枯苦淡泊。处之无所难。仆欲买绳屦。侯怒曰。奈何不自为草屦。而求买绳屦为。日责令捆一屦。每主吏供物。物少即喜。物多即嚬蹙。余方馆于吏家。每闻吏相与语。不以私怒怒我辈者。此侯而已。侯为政三年。节蓄有馀财。庸以赡学资。蠲里徭。补吏饩。为惠甚多。然余姑略其惠而详其俭。惟俭所以能惠也。抑余自来此后。固不敢以朝夕之须累侯。而侯时时载酒携鱼。扶杖而过枉。所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则有日矣。独又有感者。顷值侯之生辰。致盛食于余。余所居。有远近来学者数人。时方天寒雪作。余呼与共饮。方行酒。见小吏疾走至。而厨传者踵其后。吏将侯命曰。寄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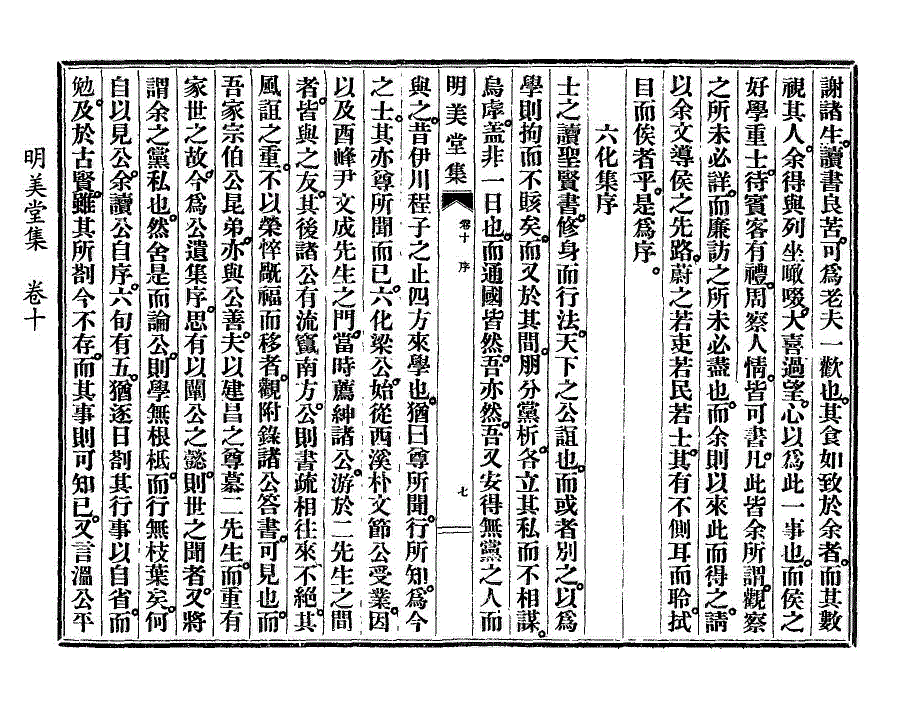 谢诸生。读书良苦。可为老夫一欢也。其食如致于余者。而其数视其人。余得与列坐啖啜。大喜过望。心以为此一事也。而侯之好学重士。待宾客有礼。周察人情。皆可书。凡此皆余所谓。观察之所未必详。而廉访之所未必尽也。而余则以来此而得之。请以余文导侯之先路。蔚之若吏若民若士。其有不侧耳而聆。拭目而俟者乎。是为序。
谢诸生。读书良苦。可为老夫一欢也。其食如致于余者。而其数视其人。余得与列坐啖啜。大喜过望。心以为此一事也。而侯之好学重士。待宾客有礼。周察人情。皆可书。凡此皆余所谓。观察之所未必详。而廉访之所未必尽也。而余则以来此而得之。请以余文导侯之先路。蔚之若吏若民若士。其有不侧耳而聆。拭目而俟者乎。是为序。六化集序
士之读圣贤书。修身而行法。天下之公谊也。而或者别之。以为学则拘而不赅矣。而又于其间。朋分党析。各立其私而不相谋。乌虖。盖非一日也。而通国皆然。吾亦然。吾又安得无党之人而与之。昔伊川程子之止四方来学也。犹曰尊所闻。行所知。为今之士。其亦尊所闻而已。六化梁公。始从西溪朴文节公受业。因以及酉峰尹文成先生之门。当时荐绅诸公。游于二先生之间者。皆与之友。其后诸公有流窜南方。公则书疏相往来不绝。其风谊之重。不以荣悴祸福而移者。观附录诸公答书。可见也。而吾家宗伯公昆弟。亦与公善。夫以建昌之尊慕二先生。而重有家世之故。今为公遗集序。思有以阐公之懿。则世之闻者。又将谓余之党私也。然舍是而论公。则学无根柢。而行无枝叶矣。何自以见公。余读公自序。六旬有五。犹逐日劄其行事以自省。而勉。及于古贤。虽其所劄今不存。而其事则可知已。又言温公平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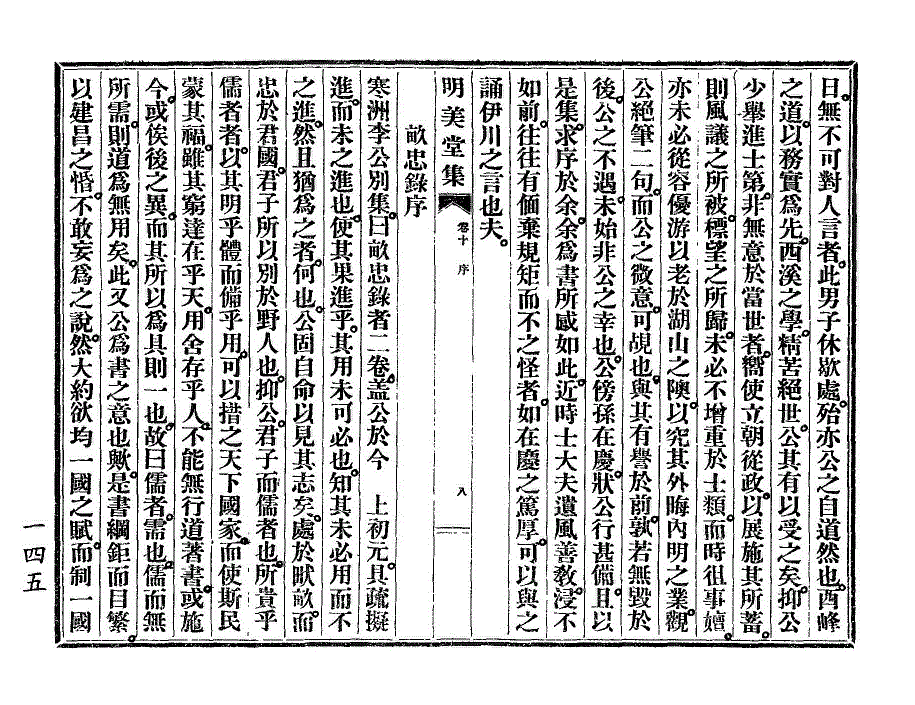 日。无不可对人言者。此男子休歇处。殆亦公之自道然也。酉峰之道。以务实为先。西溪之学。精苦绝世。公其有以受之矣。抑公少举进士第。非无意于当世者。向使立朝从政。以展施其所蓄。则风议之所被。标望之所归。未必不增重于士类。而时徂事嬗。亦未必从容优游以老于湖山之隩。以究其外晦内明之业。观公绝笔二句。而公之微意。可觇也。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公之不遇。未始非公之幸也。公傍孙在庆。状公行甚备。且以是集。求序于余。余为书所感如此。近时士大夫遗风善教。浸不如前。往往有偭弃规矩而不之怪者。如在庆之笃厚。可以与之诵伊川之言也夫。
日。无不可对人言者。此男子休歇处。殆亦公之自道然也。酉峰之道。以务实为先。西溪之学。精苦绝世。公其有以受之矣。抑公少举进士第。非无意于当世者。向使立朝从政。以展施其所蓄。则风议之所被。标望之所归。未必不增重于士类。而时徂事嬗。亦未必从容优游以老于湖山之隩。以究其外晦内明之业。观公绝笔二句。而公之微意。可觇也。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公之不遇。未始非公之幸也。公傍孙在庆。状公行甚备。且以是集。求序于余。余为书所感如此。近时士大夫遗风善教。浸不如前。往往有偭弃规矩而不之怪者。如在庆之笃厚。可以与之诵伊川之言也夫。亩忠录序
寒洲李公别集。曰亩忠录者二卷。盖公于今 上初元。具疏拟进。而未之进也。使其果进乎。其用未可必也。知其未必用而不之进。然且犹为之者。何也。公固自命以见其志矣。处于畎亩。而忠于君国。君子所以别于野人也。抑公。君子而儒者也。所贵乎儒者者。以其明乎体而备乎用。可以措之天下国家。而使斯民蒙其福。虽其穷达在乎天。用舍存乎人。不能无行道著书。或施今。或俟后之异。而其所以为具则一也。故曰儒者。需也。儒而无所需。则道为无用矣。此又公为书之意也欤。是书纲钜而目繁。以建昌之惛。不敢妄为之说。然大约欲均一国之赋。而制一国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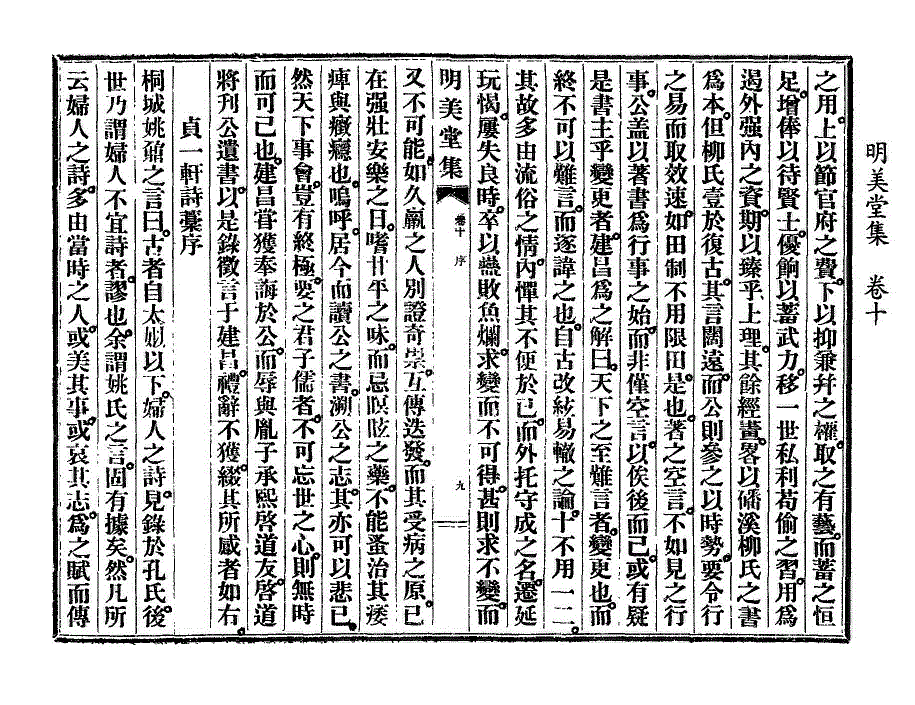 之用。上以节官府之费。下以抑兼并之权。取之有艺。而蓄之恒足。增俸以待贤士。优饷以蓄武力。移一世私利苟偷之习。用为遏外强内之资。期以臻乎上理。其馀经画。略以磻溪柳氏之书为本。但柳氏壹于复古。其言阔远。而公则参之以时势。要令行之易而取效速。如田制不用限田。是也。著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公盖以著书为行事之始。而非仅空言。以俟后而已。或有疑是书主乎变更者。建昌为之解曰。天下之至难言者。变更也。而终不可以难言。而遂讳之也。自古改弦易辙之论。十不用一二。其故多由流俗之情。内惮其不便于己。而外托守成之名。迁延玩愒。屡失良时。卒以蛊败鱼烂。求变而不可得。甚则求不变。而又不可能。如久羸之人别證奇祟。互传迭发。而其受病之原。已在强壮安乐之日。嗜甘平之味。而忌瞑眩之药。不能蚤治其痿痹与症瘾也。呜呼。居今而读公之书。溯公之志。其亦可以悲已。然天下事会。岂有终极。要之君子儒者。不可忘世之心。则无时而可已也。建昌尝获奉诲于公。而辱与胤子承熙启道友。启道将刊公遗书。以是录徵言于建昌。礼辞不获。缀其所感者如右。
之用。上以节官府之费。下以抑兼并之权。取之有艺。而蓄之恒足。增俸以待贤士。优饷以蓄武力。移一世私利苟偷之习。用为遏外强内之资。期以臻乎上理。其馀经画。略以磻溪柳氏之书为本。但柳氏壹于复古。其言阔远。而公则参之以时势。要令行之易而取效速。如田制不用限田。是也。著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公盖以著书为行事之始。而非仅空言。以俟后而已。或有疑是书主乎变更者。建昌为之解曰。天下之至难言者。变更也。而终不可以难言。而遂讳之也。自古改弦易辙之论。十不用一二。其故多由流俗之情。内惮其不便于己。而外托守成之名。迁延玩愒。屡失良时。卒以蛊败鱼烂。求变而不可得。甚则求不变。而又不可能。如久羸之人别證奇祟。互传迭发。而其受病之原。已在强壮安乐之日。嗜甘平之味。而忌瞑眩之药。不能蚤治其痿痹与症瘾也。呜呼。居今而读公之书。溯公之志。其亦可以悲已。然天下事会。岂有终极。要之君子儒者。不可忘世之心。则无时而可已也。建昌尝获奉诲于公。而辱与胤子承熙启道友。启道将刊公遗书。以是录徵言于建昌。礼辞不获。缀其所感者如右。贞一轩诗藁序
桐城姚鼐之言曰。古者自太姒以下。妇人之诗。见录于孔氏。后世乃谓妇人不宜诗者。谬也。余谓姚氏之言。固有据矣。然凡所云妇人之诗。多由当时之人。或美其事。或哀其志。为之赋而传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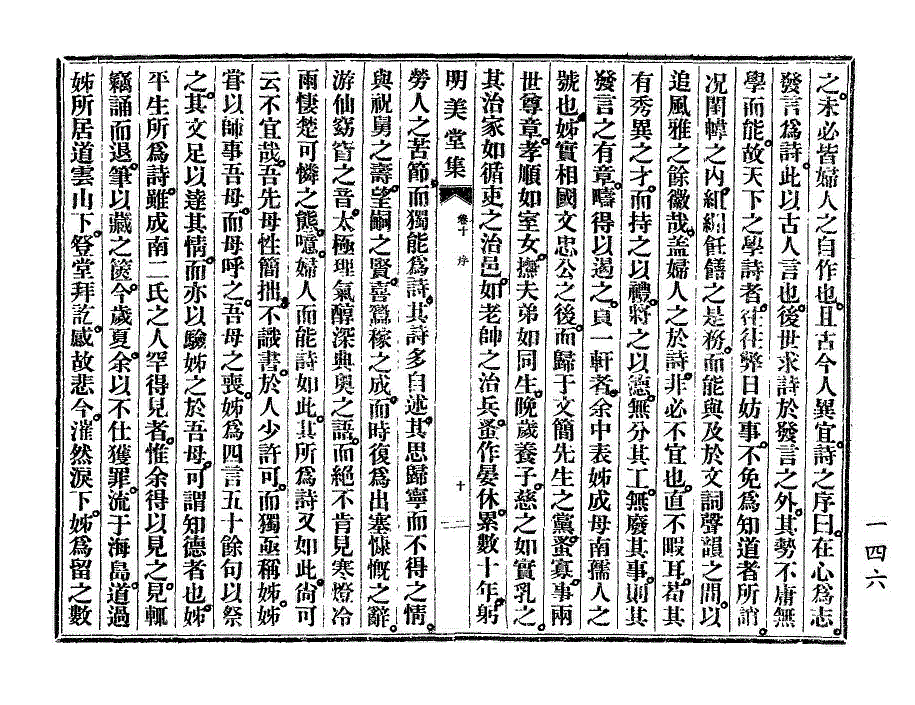 之。未必皆妇人之自作也。且古今人异宜。诗之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以古人言也。后世求诗于发言之外。其势不庸无学而能。故天下之学诗者。往往弊日妨事。不免为知道者所诮。况闺帏之内。组紃饪膳之是务。而能与及于文词声韵之间。以追风雅之馀徽哉。盖妇人之于诗。非必不宜也。直不暇耳。苟其有秀异之才。而持之以礼。将之以德。无分其工。无废其事。则其发言之有章。畴得以遏之。贞一轩者。余中表姊成母南孺人之号也。姊实相国文忠公之后。而归于文简先生之党。蚤寡。事两世尊章。孝顺如室女。抚夫弟如同生。晚岁养子。慈之如实乳之。其治家如循吏之治邑。如老帅之治兵。蚤作晏休。累数十年。躬劳人之苦节。而独能为诗。其诗多自述。其思归宁而不得之情。与祝舅之寿。望嗣之贤。喜蚕稼之成。而时复为出塞慷慨之辞。游仙窈窅之音。太极理气醇深典奥之语。而绝不肯见寒灯冷雨悽楚可怜之熊。噫。妇人而能诗如此。其所为诗又如此。尚可云不宜哉。吾先母性简拙。不识书。于人少许可。而独亟称姊。姊尝以师事吾母。而母呼之。吾母之丧。姊为四言五十馀句以祭之。其文足以达其情。而亦以验姊之于吾母。可谓知德者也。姊平生所为诗。虽成南二氏之人罕得见者。惟余得以见之。见辄窃诵而退。笔以藏之箧。今岁夏。余以不仕获罪。流于海岛。道过姊所居道云山下。登堂拜讫。感故悲今。漼然泪下。姊为留之数
之。未必皆妇人之自作也。且古今人异宜。诗之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以古人言也。后世求诗于发言之外。其势不庸无学而能。故天下之学诗者。往往弊日妨事。不免为知道者所诮。况闺帏之内。组紃饪膳之是务。而能与及于文词声韵之间。以追风雅之馀徽哉。盖妇人之于诗。非必不宜也。直不暇耳。苟其有秀异之才。而持之以礼。将之以德。无分其工。无废其事。则其发言之有章。畴得以遏之。贞一轩者。余中表姊成母南孺人之号也。姊实相国文忠公之后。而归于文简先生之党。蚤寡。事两世尊章。孝顺如室女。抚夫弟如同生。晚岁养子。慈之如实乳之。其治家如循吏之治邑。如老帅之治兵。蚤作晏休。累数十年。躬劳人之苦节。而独能为诗。其诗多自述。其思归宁而不得之情。与祝舅之寿。望嗣之贤。喜蚕稼之成。而时复为出塞慷慨之辞。游仙窈窅之音。太极理气醇深典奥之语。而绝不肯见寒灯冷雨悽楚可怜之熊。噫。妇人而能诗如此。其所为诗又如此。尚可云不宜哉。吾先母性简拙。不识书。于人少许可。而独亟称姊。姊尝以师事吾母。而母呼之。吾母之丧。姊为四言五十馀句以祭之。其文足以达其情。而亦以验姊之于吾母。可谓知德者也。姊平生所为诗。虽成南二氏之人罕得见者。惟余得以见之。见辄窃诵而退。笔以藏之箧。今岁夏。余以不仕获罪。流于海岛。道过姊所居道云山下。登堂拜讫。感故悲今。漼然泪下。姊为留之数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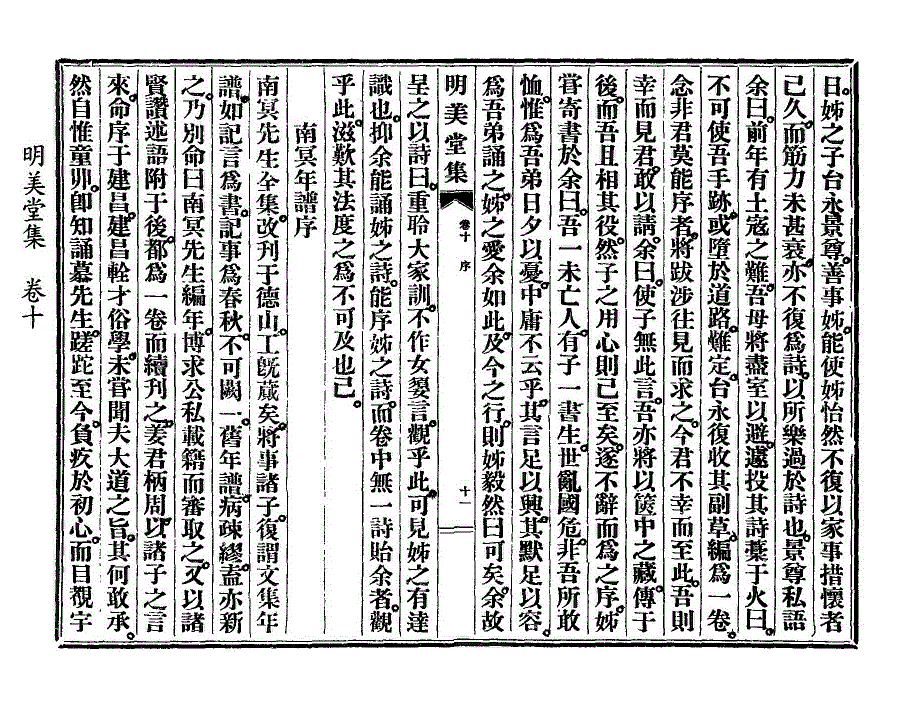 日。姊之子台永,景尊。善事姊。能使姊怡然不复以家事措怀者已久。而筋力未甚衰。亦不复为诗。以所乐过于诗也。景尊私语余曰。前年有土寇之难。吾母将尽室以避。遽投其诗藁于火曰。不可使吾手迹。或堕于道路。难定。台永复收其副草。编为一卷。念非君莫能序者。将跋涉往见而求之。今君不幸而至此。吾则幸而见君。敢以请。余曰。使子无此言。吾亦将以箧中之藏。传于后。而吾且相其役。然子之用心则已至矣。遂不辞而为之序。姊尝寄书于余曰。吾一未亡人。有子一书生。世乱国危。非吾所敢恤。惟为吾弟日夕以忧。中庸不云乎。其言足以兴。其默足以容。为吾弟诵之。姊之爱余如此。及今之行。则姊毅然曰可矣。余故呈之以诗曰。重聆大家训。不作女媭言。观乎此。可见姊之有达识也。抑余能诵姊之诗。能序姊之诗。而卷中无一诗贻余者。观乎此。滋叹其法度之为不可及也已。
日。姊之子台永,景尊。善事姊。能使姊怡然不复以家事措怀者已久。而筋力未甚衰。亦不复为诗。以所乐过于诗也。景尊私语余曰。前年有土寇之难。吾母将尽室以避。遽投其诗藁于火曰。不可使吾手迹。或堕于道路。难定。台永复收其副草。编为一卷。念非君莫能序者。将跋涉往见而求之。今君不幸而至此。吾则幸而见君。敢以请。余曰。使子无此言。吾亦将以箧中之藏。传于后。而吾且相其役。然子之用心则已至矣。遂不辞而为之序。姊尝寄书于余曰。吾一未亡人。有子一书生。世乱国危。非吾所敢恤。惟为吾弟日夕以忧。中庸不云乎。其言足以兴。其默足以容。为吾弟诵之。姊之爱余如此。及今之行。则姊毅然曰可矣。余故呈之以诗曰。重聆大家训。不作女媭言。观乎此。可见姊之有达识也。抑余能诵姊之诗。能序姊之诗。而卷中无一诗贻余者。观乎此。滋叹其法度之为不可及也已。南冥年谱序
南冥先生全集。改刊于德山。工既蒇矣。将事诸子。复谓文集年谱。如记言为书。记事为春秋。不可阙一。旧年谱。病疏缪。盍亦新之。乃别命曰南冥先生编年。博求公私载籍而审取之。又以诸贤赞述语附于后。都为一卷而续刊之。姜君柄周。以诸子之言来。命序于建昌。建昌辁才俗学。未尝闻夫大道之旨。其何敢承。然自惟童丱。即知诵慕先生。蹉跎至今。负疚于初心。而目睹宇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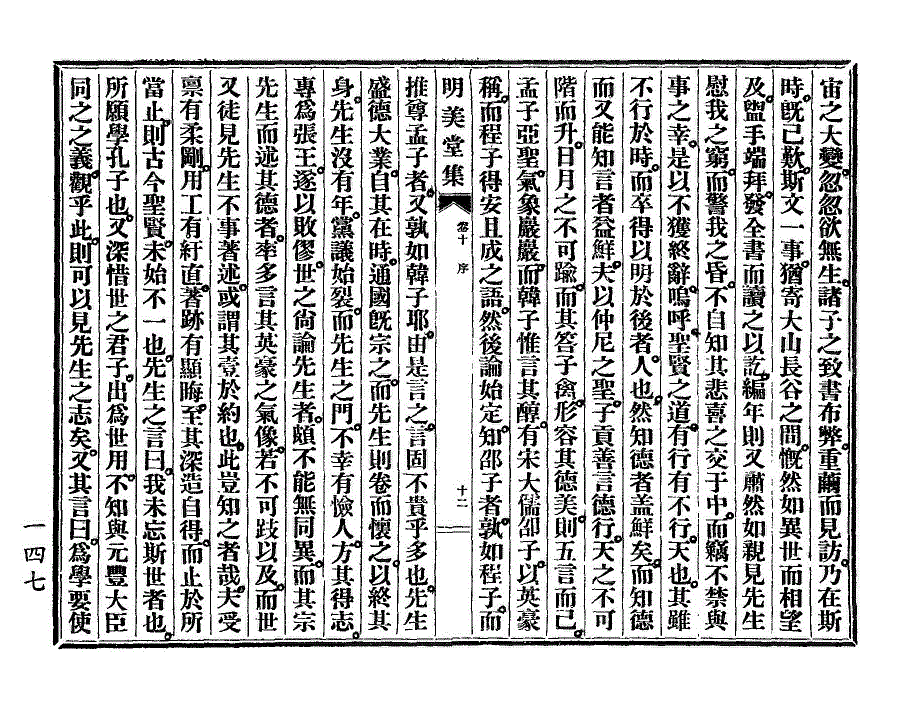 宙之大变。忽忽欲无生。诸子之致书布弊。重茧而见访。乃在斯时。既已叹。斯文一事。犹寄大山长谷之间。慨然如异世而相望及。盥手端拜。发全书而读之以讫。编年则又肃然如亲见先生慰我之穷。而警我之昏。不自知其悲喜之交于中。而窃不禁与事之幸。是以不获终辞。呜呼。圣贤之道。有行有不行。天也。其虽不行于时。而卒得以明于后者。人也。然知德者盖鲜矣。而知德而又能知言者益鲜。夫以仲尼之圣。子贡善言德行。天之不可阶而升。日月之不可踰。而其答子禽。形容其德美。则五言而已。孟子亚圣。气象岩岩。而韩子惟言其醇。有宋大儒邵子。以英豪称。而程子得安且成之语。然后论始定。知邵子者。孰如程子。而推尊孟子者。又孰如韩子耶。由是言之。言固不贵乎多也。先生盛德大业。自其在时。通国既宗之。而先生则卷而怀之。以终其身。先生没有年。党议始裂。而先生之门。不幸有憸人。方其得志。专为张王。遂以败僇。世之尚论先生者。颇不能无同异。而其宗先生而述其德者。率多言其英豪之气像。若不可跂以及。而世又徒见先生不事著述。或谓其壹于约也。此岂知之者哉。夫受禀有柔刚。用工有纡直。著迹有显晦。至其深造自得。而止于所当止。则古今圣贤。未始不一也。先生之言曰。我未忘斯世者也。所愿学孔子也。又深惜世之君子。出为世用。不知与元丰大臣同之之义。观乎此。则可以见先生之志矣。又其言曰。为学要使
宙之大变。忽忽欲无生。诸子之致书布弊。重茧而见访。乃在斯时。既已叹。斯文一事。犹寄大山长谷之间。慨然如异世而相望及。盥手端拜。发全书而读之以讫。编年则又肃然如亲见先生慰我之穷。而警我之昏。不自知其悲喜之交于中。而窃不禁与事之幸。是以不获终辞。呜呼。圣贤之道。有行有不行。天也。其虽不行于时。而卒得以明于后者。人也。然知德者盖鲜矣。而知德而又能知言者益鲜。夫以仲尼之圣。子贡善言德行。天之不可阶而升。日月之不可踰。而其答子禽。形容其德美。则五言而已。孟子亚圣。气象岩岩。而韩子惟言其醇。有宋大儒邵子。以英豪称。而程子得安且成之语。然后论始定。知邵子者。孰如程子。而推尊孟子者。又孰如韩子耶。由是言之。言固不贵乎多也。先生盛德大业。自其在时。通国既宗之。而先生则卷而怀之。以终其身。先生没有年。党议始裂。而先生之门。不幸有憸人。方其得志。专为张王。遂以败僇。世之尚论先生者。颇不能无同异。而其宗先生而述其德者。率多言其英豪之气像。若不可跂以及。而世又徒见先生不事著述。或谓其壹于约也。此岂知之者哉。夫受禀有柔刚。用工有纡直。著迹有显晦。至其深造自得。而止于所当止。则古今圣贤。未始不一也。先生之言曰。我未忘斯世者也。所愿学孔子也。又深惜世之君子。出为世用。不知与元丰大臣同之之义。观乎此。则可以见先生之志矣。又其言曰。为学要使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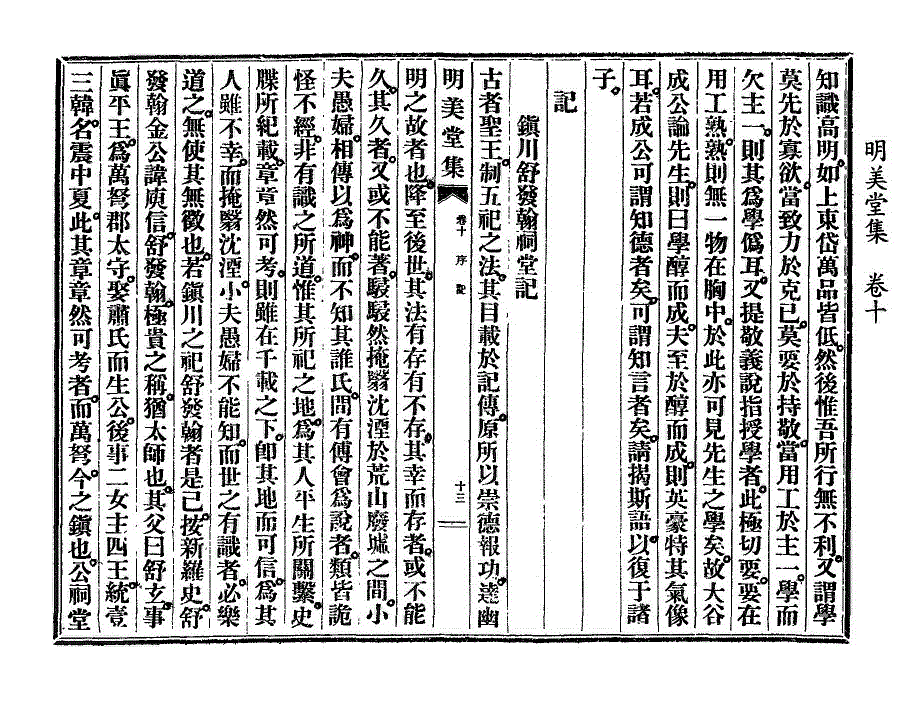 知识高明。如上东岱万品皆低。然后惟吾所行无不利。又谓学莫先于寡欲。当致力于克己。莫要于持敬。当用工于主一。学而欠主一。则其为学伪耳。又提敬义说指授学者。此极切要。要在用工熟。熟则无一物在胸中。于此亦可见先生之学矣。故大谷成公论先生。则曰学醇而成。夫至于醇而成。则英豪特其气像耳。若成公可谓知德者矣。可谓知言者矣。请揭斯语。以复于诸子。
知识高明。如上东岱万品皆低。然后惟吾所行无不利。又谓学莫先于寡欲。当致力于克己。莫要于持敬。当用工于主一。学而欠主一。则其为学伪耳。又提敬义说指授学者。此极切要。要在用工熟。熟则无一物在胸中。于此亦可见先生之学矣。故大谷成公论先生。则曰学醇而成。夫至于醇而成。则英豪特其气像耳。若成公可谓知德者矣。可谓知言者矣。请揭斯语。以复于诸子。明美堂集卷十(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记
镇川舒发翰祠堂记
古者圣王。制五祀之法。其目载于记传。原所以崇德报功。达幽明之故者也。降至后世。其法有存有不存。其幸而存者。或不能久。其久者。又或不能著。骎骎然掩翳沈湮于荒山废墟之间。小夫愚妇。相传以为神。而不知其谁氏。间有傅会为说者。类皆诡怪不经。非有识之所道。惟其所祀之地。为其人平生所关系。史牒所纪载。章章然可考。则虽在千载之下。即其地而可信。为其人虽不幸。而掩翳沈湮。小夫愚妇不能知。而世之有识者。必乐道之。无使其无徵也。若镇川之祀舒发翰者是已。按新罗史。舒发翰金公讳庾信。舒发翰。极贵之称。犹太师也。其父曰舒玄。事真平王。为万弩郡太守。娶肃氏而生公。后事二女主四王。统壹三韩。名震中夏。此其章章然可考者。而万弩。今之镇也。公祠堂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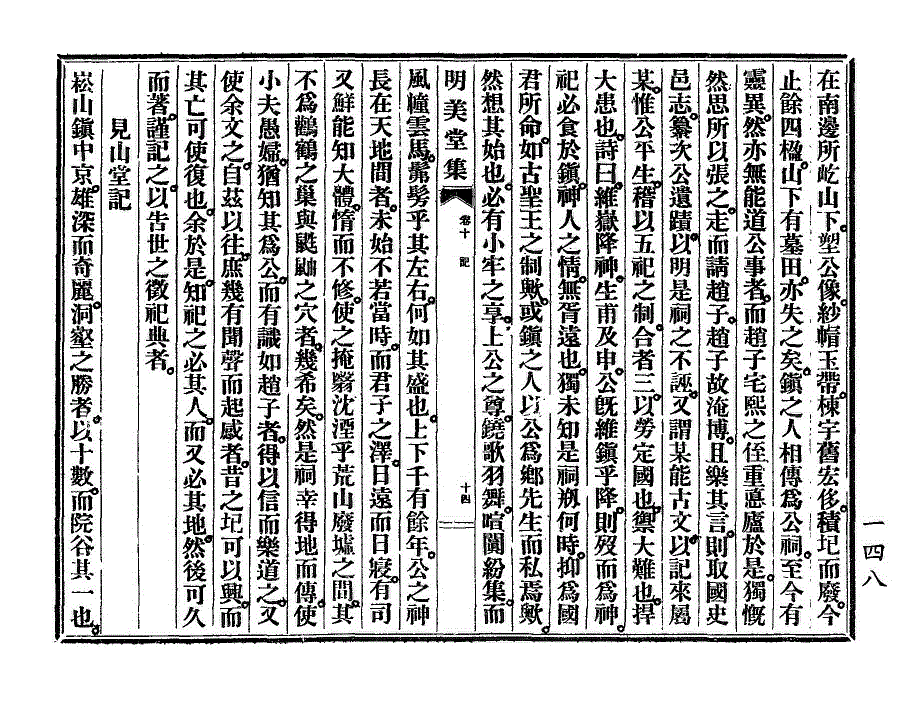 在南边所屹山下。塑公像。纱帽玉带。栋宇旧宏侈。积圮而废。今止馀四楹。山下有墓田。亦失之矣。镇之人相传为公祠。至今有灵异。然亦无能道公事者。而赵子宅熙之侄重德庐于是。独慨然思所以张之。走而请赵子。赵子故淹博。且乐其言。则取国史邑志。纂次公遗迹。以明是祠之不诬。又谓某能古文。以记来属某。惟公平生。稽以五祀之制。合者三。以劳定国也。御大难也。捍大患也。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公既维镇乎降。则殁而为神。祀必食于镇。神人之情。无胥远也。独未知是祠刱何时。抑为国君所命。如古圣王之制欤。或镇之人以公为乡先生而私焉欤。然想其始也。必有小牢之享。上公之尊。铙歌羽舞。喧阗纷集。而风幢云马。髴髣乎其左右。何如其盛也。上下千有馀年。公之神长在天地间者。未始不若当时。而君子之泽。日远而日寝。有司又鲜能知大体。惰而不修。使之掩翳沈湮乎荒山废墟之间。其不为鹳鹤之巢与鼪鼬之穴者。几希矣。然是祠幸得地而传。使小夫愚妇。犹知其为公。而有识如赵子者。得以信而乐道之。又使余文之。自兹以往。庶几有闻声而起感者。昔之圮可以兴。而其亡可使复也。余于是。知祀之必其人。而又必其地。然后可久而著。谨记之。以告世之徵祀典者。
在南边所屹山下。塑公像。纱帽玉带。栋宇旧宏侈。积圮而废。今止馀四楹。山下有墓田。亦失之矣。镇之人相传为公祠。至今有灵异。然亦无能道公事者。而赵子宅熙之侄重德庐于是。独慨然思所以张之。走而请赵子。赵子故淹博。且乐其言。则取国史邑志。纂次公遗迹。以明是祠之不诬。又谓某能古文。以记来属某。惟公平生。稽以五祀之制。合者三。以劳定国也。御大难也。捍大患也。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公既维镇乎降。则殁而为神。祀必食于镇。神人之情。无胥远也。独未知是祠刱何时。抑为国君所命。如古圣王之制欤。或镇之人以公为乡先生而私焉欤。然想其始也。必有小牢之享。上公之尊。铙歌羽舞。喧阗纷集。而风幢云马。髴髣乎其左右。何如其盛也。上下千有馀年。公之神长在天地间者。未始不若当时。而君子之泽。日远而日寝。有司又鲜能知大体。惰而不修。使之掩翳沈湮乎荒山废墟之间。其不为鹳鹤之巢与鼪鼬之穴者。几希矣。然是祠幸得地而传。使小夫愚妇。犹知其为公。而有识如赵子者。得以信而乐道之。又使余文之。自兹以往。庶几有闻声而起感者。昔之圮可以兴。而其亡可使复也。余于是。知祀之必其人。而又必其地。然后可久而著。谨记之。以告世之徵祀典者。见山堂记
崧山镇中京。雄深而奇丽。洞壑之胜者。以十数。而院谷其一也。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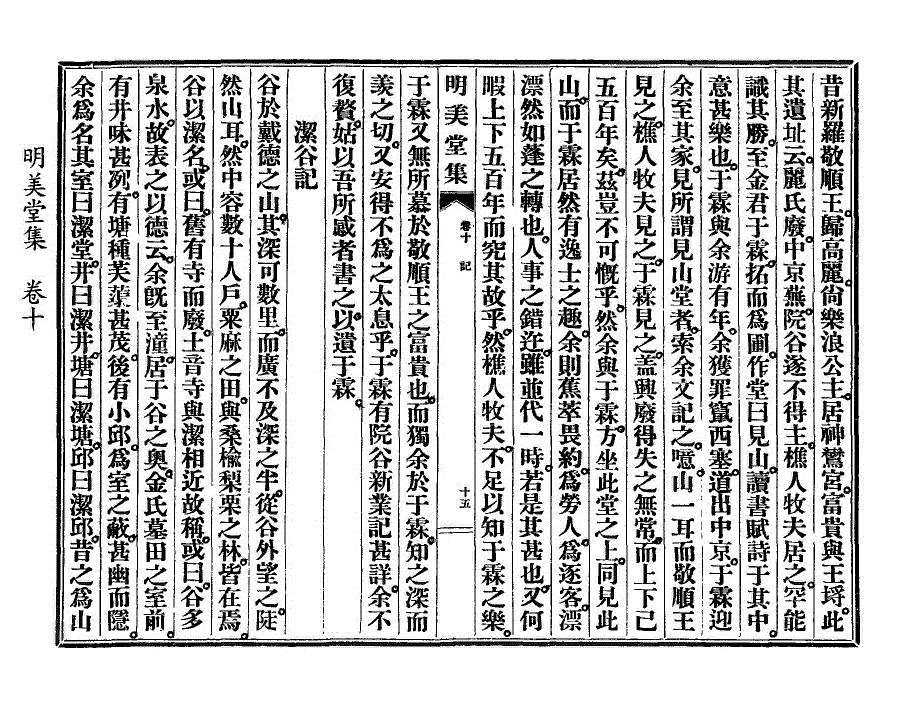 昔新罗敬顺王。归高丽。尚乐浪公主。居神鸾宫。富贵与王埒。此其遗址云。丽氏废。中京芜。院谷遂不得主。樵人牧夫居之。罕能识其胜。至金君于霖。拓而为圃。作堂曰见山。读书赋诗于其中。意甚乐也。于霖与余游有年。余获罪窜西塞。道出中京。于霖迎余至其家。见所谓见山堂者。索余文记之。噫。山一耳而敬顺王见之。樵人牧夫见之。于霖见之。盖兴废得失之无常。而上下已五百年矣。兹岂不可慨乎。然余与于霖。方坐此堂之上。同见此山。而于霖居然有逸士之趣。余则蕉萃畏约。为劳人。为逐客。漂漂然如蓬之转也。人事之错迕。虽并代一时。若是其甚也。又何暇上下五百年而究其故乎。然樵人牧夫。不足以知于霖之乐。于霖又无所慕于敬顺王之富贵也。而独余于于霖。知之深而羡之切。又安得不为之太息乎。于霖有院谷新业记甚详。余不复赘。姑以吾所感者书之。以遗于霖。
昔新罗敬顺王。归高丽。尚乐浪公主。居神鸾宫。富贵与王埒。此其遗址云。丽氏废。中京芜。院谷遂不得主。樵人牧夫居之。罕能识其胜。至金君于霖。拓而为圃。作堂曰见山。读书赋诗于其中。意甚乐也。于霖与余游有年。余获罪窜西塞。道出中京。于霖迎余至其家。见所谓见山堂者。索余文记之。噫。山一耳而敬顺王见之。樵人牧夫见之。于霖见之。盖兴废得失之无常。而上下已五百年矣。兹岂不可慨乎。然余与于霖。方坐此堂之上。同见此山。而于霖居然有逸士之趣。余则蕉萃畏约。为劳人。为逐客。漂漂然如蓬之转也。人事之错迕。虽并代一时。若是其甚也。又何暇上下五百年而究其故乎。然樵人牧夫。不足以知于霖之乐。于霖又无所慕于敬顺王之富贵也。而独余于于霖。知之深而羡之切。又安得不为之太息乎。于霖有院谷新业记甚详。余不复赘。姑以吾所感者书之。以遗于霖。洁谷记
谷于戴德之山。其深可数里。而广不及深之半。从谷外望之。陡然山耳。然中容数十人户。粟麻之田。与桑榆梨栗之林。皆在焉。谷以洁名。或曰。旧有寺而废。土音寺与洁相近故称。或曰。谷多泉水。故表之以德云。余既至潼。居于谷之奥。金氏墓田之室前。有井味甚冽。有塘种芙蕖甚茂。后有小邱。为室之蔽。甚幽而隐。余为名其室曰洁堂。井曰洁井。塘曰洁塘。邱曰洁邱。昔之为山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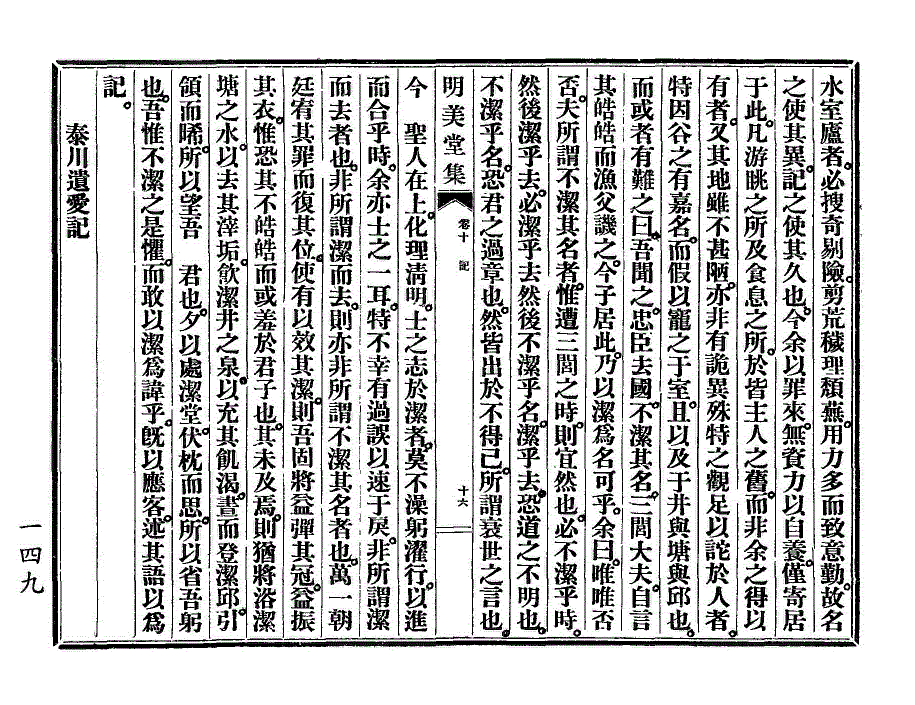 水室庐者。必搜奇剔险。剪荒秽理颓芜。用力多而致意勤。故名之使其异。记之使其久也。今余以罪来。无资力以自养。仅寄居于此。凡游眺之所及食息之所。于皆主人之旧。而非余之得以有者。又其地虽不甚陋。亦非有诡异殊特之观足以詑于人者。特因谷之有嘉名。而假以宠之于室。且以及于井与塘与邱也。而或者有难之曰。吾闻之。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三闾大夫。自言其皓皓而渔父讥之。今子居此。乃以洁为名可乎。余曰。唯唯否否。夫所谓不洁其名者。惟遭三闾之时。则宜然也。必不洁乎时。然后洁乎去。必洁乎去然后不洁乎名。洁乎去。恐道之不明也。不洁乎名。恐君之过章也。然皆出于不得已。所谓衰世之言也。今 圣人在上。化理清明。士之志于洁者。莫不澡躬濯行。以进而合乎时。余亦士之一耳。特不幸有过误以速于戾。非所谓洁而去者也。非所谓洁而去。则亦非所谓不洁其名者也。万一朝廷宥其罪而复其位。使有以效其洁。则吾固将益弹其冠。益振其衣。惟恐其不皓皓而或羞于君子也。其未及焉。则犹将浴洁塘之水。以去其滓垢。饮洁井之泉。以充其饥渴。昼而登洁邱。引领而晞。所以望吾 君也。夕以处洁堂。伏枕而思。所以省吾躬也。吾惟不洁之是惧。而敢以洁为讳乎。既以应客。述其语以为记。
水室庐者。必搜奇剔险。剪荒秽理颓芜。用力多而致意勤。故名之使其异。记之使其久也。今余以罪来。无资力以自养。仅寄居于此。凡游眺之所及食息之所。于皆主人之旧。而非余之得以有者。又其地虽不甚陋。亦非有诡异殊特之观足以詑于人者。特因谷之有嘉名。而假以宠之于室。且以及于井与塘与邱也。而或者有难之曰。吾闻之。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三闾大夫。自言其皓皓而渔父讥之。今子居此。乃以洁为名可乎。余曰。唯唯否否。夫所谓不洁其名者。惟遭三闾之时。则宜然也。必不洁乎时。然后洁乎去。必洁乎去然后不洁乎名。洁乎去。恐道之不明也。不洁乎名。恐君之过章也。然皆出于不得已。所谓衰世之言也。今 圣人在上。化理清明。士之志于洁者。莫不澡躬濯行。以进而合乎时。余亦士之一耳。特不幸有过误以速于戾。非所谓洁而去者也。非所谓洁而去。则亦非所谓不洁其名者也。万一朝廷宥其罪而复其位。使有以效其洁。则吾固将益弹其冠。益振其衣。惟恐其不皓皓而或羞于君子也。其未及焉。则犹将浴洁塘之水。以去其滓垢。饮洁井之泉。以充其饥渴。昼而登洁邱。引领而晞。所以望吾 君也。夕以处洁堂。伏枕而思。所以省吾躬也。吾惟不洁之是惧。而敢以洁为讳乎。既以应客。述其语以为记。泰川遗爱记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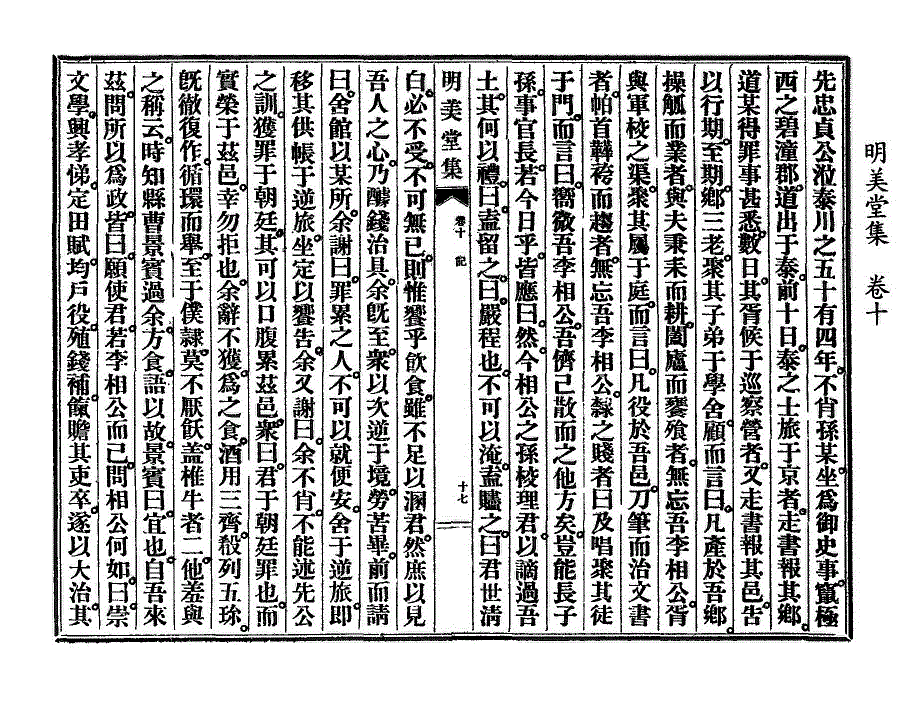 先忠贞公涖泰川之五十有四年。不肖孙某。坐为御史事。窜极西之碧潼郡。道出于泰。前十日。泰之士旅于京者。走书报其乡。道某得罪事甚悉。数日。其胥候于巡察营者。又走书报其邑。告以行期。至期。乡三老。聚其子弟于学舍。顾而言曰。凡产于吾乡。操觚而业者。与夫秉耒而耕。阖庐而饔飧者。无忘吾李相公。胥与军校之渠。聚其属于庭。而言曰。凡役于吾邑。刀笔而治文书者。帕首靴裤而趋者。无忘吾李相公。隶之贱者曰及唱聚其徒于门。而言曰。向微吾李相公。吾侪已散而之他方矣。岂能长子孙。事官长。若今日乎。皆应曰。然。今相公之孙校理君。以谪过吾土。其何以礼。曰。盍留之。曰。严程也。不可以淹。盍赆之。曰君世清白。必不受。不可无已。则惟飨乎饮食。虽不足以溷君。然庶以见吾人之心。乃醵钱治具。余既至。众以次逆于境。劳苦毕。前而请曰。舍馆以某所。余谢曰。罪累之人。不可以就便安。舍于逆旅。即移其供帐于逆旅。坐定以飨告。余又谢曰。余不肖。不能述先公之训。获罪于朝廷。其可以口腹累兹邑。众曰。君于朝廷罪也。而实荣于兹邑。幸勿拒也。余辞不获。为之食。酒用三齐。殽列五珍。既彻复作。循环而举。至于仆隶。莫不厌饫。盖椎牛者二。他羞与之称云。时知县曹景宾过余。方食。语以故。景宾曰。宜也。自吾来兹。问所以为政。皆曰。愿使君。若李相公而已。问相公何如。曰。崇文学。兴孝悌。定田赋。均户役。殖钱补。饩赡其吏卒。遂以大治。其
先忠贞公涖泰川之五十有四年。不肖孙某。坐为御史事。窜极西之碧潼郡。道出于泰。前十日。泰之士旅于京者。走书报其乡。道某得罪事甚悉。数日。其胥候于巡察营者。又走书报其邑。告以行期。至期。乡三老。聚其子弟于学舍。顾而言曰。凡产于吾乡。操觚而业者。与夫秉耒而耕。阖庐而饔飧者。无忘吾李相公。胥与军校之渠。聚其属于庭。而言曰。凡役于吾邑。刀笔而治文书者。帕首靴裤而趋者。无忘吾李相公。隶之贱者曰及唱聚其徒于门。而言曰。向微吾李相公。吾侪已散而之他方矣。岂能长子孙。事官长。若今日乎。皆应曰。然。今相公之孙校理君。以谪过吾土。其何以礼。曰。盍留之。曰。严程也。不可以淹。盍赆之。曰君世清白。必不受。不可无已。则惟飨乎饮食。虽不足以溷君。然庶以见吾人之心。乃醵钱治具。余既至。众以次逆于境。劳苦毕。前而请曰。舍馆以某所。余谢曰。罪累之人。不可以就便安。舍于逆旅。即移其供帐于逆旅。坐定以飨告。余又谢曰。余不肖。不能述先公之训。获罪于朝廷。其可以口腹累兹邑。众曰。君于朝廷罪也。而实荣于兹邑。幸勿拒也。余辞不获。为之食。酒用三齐。殽列五珍。既彻复作。循环而举。至于仆隶。莫不厌饫。盖椎牛者二。他羞与之称云。时知县曹景宾过余。方食。语以故。景宾曰。宜也。自吾来兹。问所以为政。皆曰。愿使君。若李相公而已。问相公何如。曰。崇文学。兴孝悌。定田赋。均户役。殖钱补。饩赡其吏卒。遂以大治。其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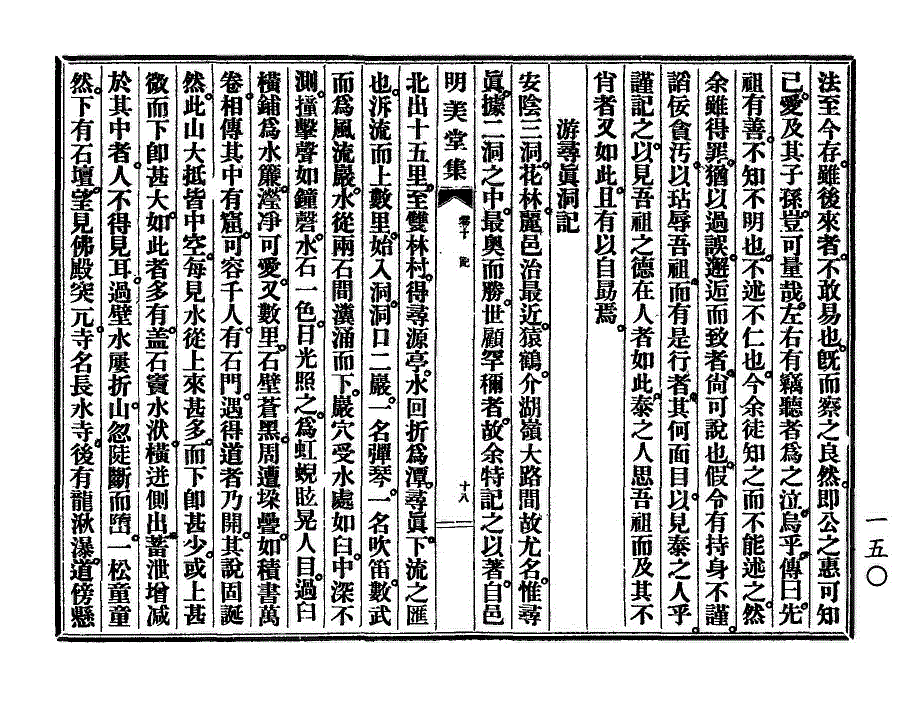 法至今存。虽后来者。不敢易也。既而察之良然。即公之惠可知已。爱及其子孙。岂可量哉。左右有窃听者为之泣。乌乎。传曰。先祖有善。不知不明也。不述不仁也。今余徒知之而不能述之。然余虽得罪。犹以过误。邂逅而致者。尚可说也。假令有持身不谨。谄佞贪污。以玷辱吾祖。而有是行者。其何面目。以见泰之人乎。谨记之。以见吾祖之德在人者如此。泰之人思吾祖而及其不肖者又如此。且有以自勖焉。
法至今存。虽后来者。不敢易也。既而察之良然。即公之惠可知已。爱及其子孙。岂可量哉。左右有窃听者为之泣。乌乎。传曰。先祖有善。不知不明也。不述不仁也。今余徒知之而不能述之。然余虽得罪。犹以过误。邂逅而致者。尚可说也。假令有持身不谨。谄佞贪污。以玷辱吾祖。而有是行者。其何面目。以见泰之人乎。谨记之。以见吾祖之德在人者如此。泰之人思吾祖而及其不肖者又如此。且有以自勖焉。游寻真洞记
安阴三洞。花林。丽邑治最近。猿鹤。介湖岭大路间故尤名。惟寻真。据二洞之中。最奥而胜。世顾罕称者。故余特记之以著。自邑北出十五里。至双林村。得寻源亭。水回折为潭。寻真。下流之汇也。溯流而上数里。始入洞。洞口二岩。一名弹琴。一名吹笛。数武而为风流岩。水从两石间瀵涌而下。岩穴受水处如臼。中深不测。撞击声如钟磬。水石一色。日光照之。为虹蜺眩晃人目。过臼横铺为水帘。滢净可爱。又数里。石壁苍黑。周遭垛叠。如积书万卷。相传其中有窟。可容千人。有石门。遇得道者乃开。其说固诞然。此山大抵皆中空。每见水从上来甚多。而下即甚少。或上甚微而下即甚大。如此者多有。盖石窦水洑。横迸侧出。蓄泄增减于其中者。人不得见耳。过壁水屡折。山忽陡断而嶞。一松童童然。下有石坛。望见佛殿突兀。寺名长水寺。后有龙湫瀑。道傍悬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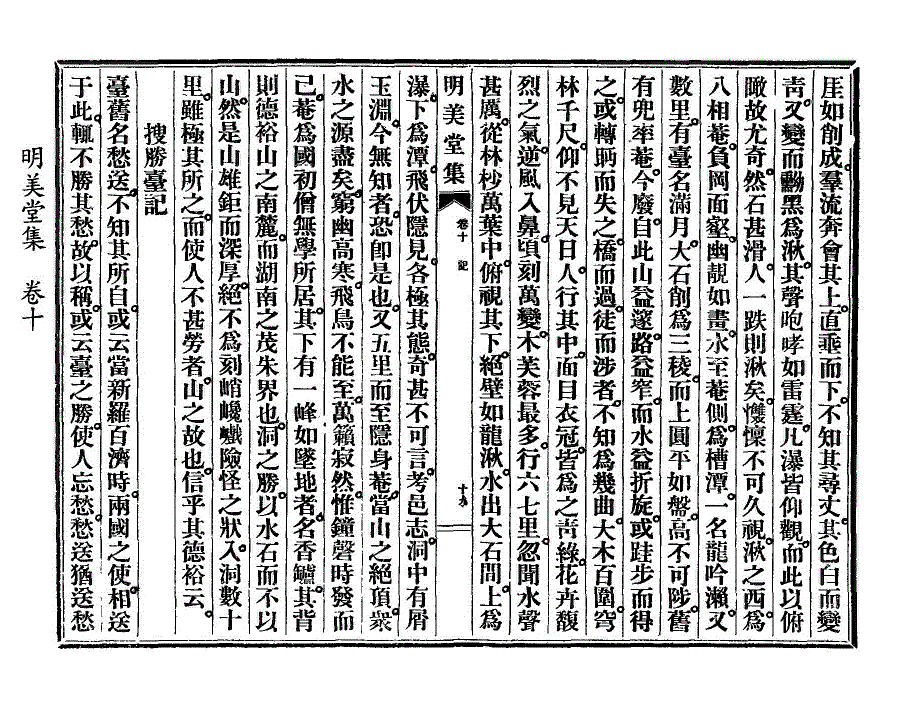 厓如削成。群流奔会其上。直垂而下。不知其寻丈。其色白而变青。又变而黝黑为湫。其声咆哮如雷霆。凡瀑皆仰观。而此以俯瞰故尤奇。然石甚滑。人一跌则湫矣。𢥠懔不可久视。湫之西。为八相庵。负冈面壑。幽靓如画。水至庵侧。为槽潭。一名龙吟濑。又数里。有台名满月。大石削为三棱。而上圆平如盘。高不可陟。旧有兜率庵。今废。自此山益邃。路益窄。而水益折旋。或跬步而得之。或转眄而失之。桥而过。徒而涉者。不知为几曲。大木百围。穹林千尺。仰不见天日。人行其中。面目衣冠。皆为之青绿。花卉馥烈之气。逆风入鼻。顷刻万变。木芙蓉最多。行六七里。忽闻水声甚厉。从林杪万叶中。俯视其下。绝壁如龙湫。水出大石间。上为瀑。下为潭。飞伏隐见。各极其态。奇甚不可言。考邑志。洞中有屑玉渊。今无知者。恐即是也。又五里而至隐身庵。当山之绝顶。众水之源尽矣。穷幽高寒。飞鸟不能至。万籁寂然。惟钟磬时发而已。庵为国初僧无学所居。其下有一峰如坠地者。名香垆。其背则德裕山之南麓。而湖南之茂朱界也。洞之胜。以水石而不以山。然是山雄钜而深厚。绝不为刻峭巉巇险怪之状。入洞数十里。虽极其所之。而使人不甚劳者。山之故也。信乎其德裕云。
厓如削成。群流奔会其上。直垂而下。不知其寻丈。其色白而变青。又变而黝黑为湫。其声咆哮如雷霆。凡瀑皆仰观。而此以俯瞰故尤奇。然石甚滑。人一跌则湫矣。𢥠懔不可久视。湫之西。为八相庵。负冈面壑。幽靓如画。水至庵侧。为槽潭。一名龙吟濑。又数里。有台名满月。大石削为三棱。而上圆平如盘。高不可陟。旧有兜率庵。今废。自此山益邃。路益窄。而水益折旋。或跬步而得之。或转眄而失之。桥而过。徒而涉者。不知为几曲。大木百围。穹林千尺。仰不见天日。人行其中。面目衣冠。皆为之青绿。花卉馥烈之气。逆风入鼻。顷刻万变。木芙蓉最多。行六七里。忽闻水声甚厉。从林杪万叶中。俯视其下。绝壁如龙湫。水出大石间。上为瀑。下为潭。飞伏隐见。各极其态。奇甚不可言。考邑志。洞中有屑玉渊。今无知者。恐即是也。又五里而至隐身庵。当山之绝顶。众水之源尽矣。穷幽高寒。飞鸟不能至。万籁寂然。惟钟磬时发而已。庵为国初僧无学所居。其下有一峰如坠地者。名香垆。其背则德裕山之南麓。而湖南之茂朱界也。洞之胜。以水石而不以山。然是山雄钜而深厚。绝不为刻峭巉巇险怪之状。入洞数十里。虽极其所之。而使人不甚劳者。山之故也。信乎其德裕云。搜胜台记
台旧名愁送。不知其所自。或云当新罗百济时。两国之使。相送于此。辄不胜其愁。故以称。或云台之胜。使人忘愁。愁送犹送愁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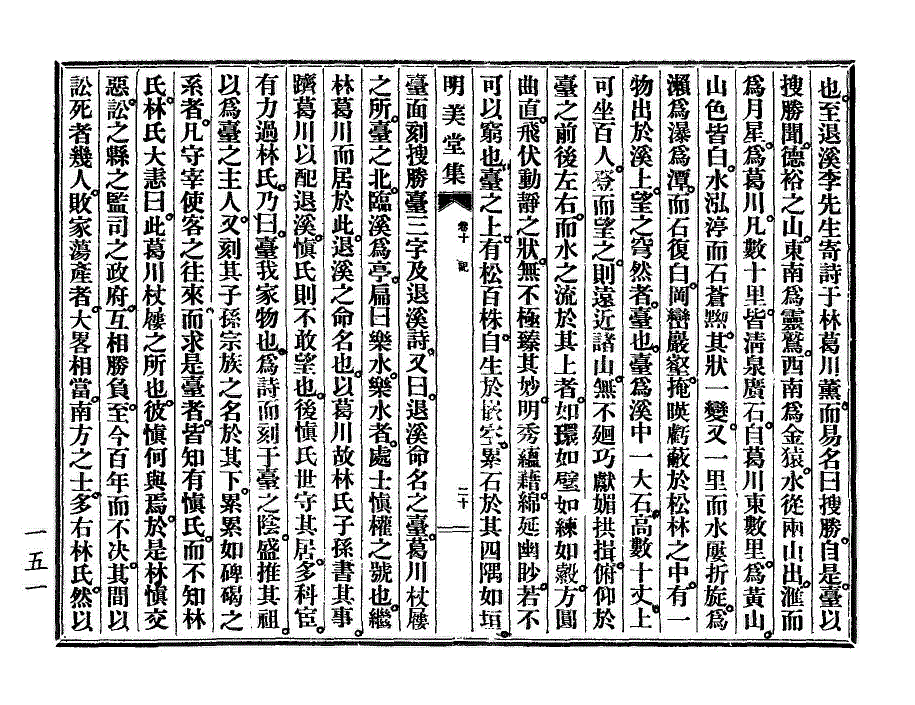 也。至退溪李先生寄诗于林葛川薰。而易名曰搜胜。自是。台以搜胜闻。德裕之山。东南为灵鹫。西南为金猿。水从两山出。汇而为月星。为葛川。凡数十里。皆清泉广石。自葛川东数里。为黄山。山色皆白。水泓淳而石苍黝。其状一变。又一里而水屡折旋。为濑为瀑为潭。而石复白。冈峦岩壑。掩映亏蔽于松林之中。有一物出于溪上。望之穹然者。台也。台为溪中一大石。高数十丈。上可坐百人。登而望之。则远近诸山。无不回巧献媚拱揖。俯仰于台之前后左右。而水之流于其上者。如环如璧如练如縠。方圆曲直。飞伏动静之状。无不极臻其妙。明秀蕴藉。绵延幽眇。若不可以穷也。台之上。有松百株。自生于嵌空。累石于其四隅如垣。台面刻搜胜台三字及退溪诗。又曰。退溪命名之台。葛川杖屦之所。台之北。临溪为亭。扁曰乐水。乐水者。处士慎权之号也。继林葛川而居于此。退溪之命名也。以葛川故林氏子孙书其事。跻葛川以配退溪。慎氏则不敢望也。后慎氏世守其居。多科宦。有力过林氏。乃曰。台我家物也。为诗而刻于台之阴。盛推其祖。以为台之主人。又刻其子孙宗族之名于其下。累累如碑碣之系者。凡守宰使客之往来。而求是台者。皆知有慎氏。而不知林氏。林氏大恚曰。此葛川杖屦之所也。彼慎何与焉。于是林慎交恶。讼之县之监司之政府。互相胜负。至今百年而不决。其间以讼死者几人。败家荡产者。大略相当。南方之士。多右林氏。然以
也。至退溪李先生寄诗于林葛川薰。而易名曰搜胜。自是。台以搜胜闻。德裕之山。东南为灵鹫。西南为金猿。水从两山出。汇而为月星。为葛川。凡数十里。皆清泉广石。自葛川东数里。为黄山。山色皆白。水泓淳而石苍黝。其状一变。又一里而水屡折旋。为濑为瀑为潭。而石复白。冈峦岩壑。掩映亏蔽于松林之中。有一物出于溪上。望之穹然者。台也。台为溪中一大石。高数十丈。上可坐百人。登而望之。则远近诸山。无不回巧献媚拱揖。俯仰于台之前后左右。而水之流于其上者。如环如璧如练如縠。方圆曲直。飞伏动静之状。无不极臻其妙。明秀蕴藉。绵延幽眇。若不可以穷也。台之上。有松百株。自生于嵌空。累石于其四隅如垣。台面刻搜胜台三字及退溪诗。又曰。退溪命名之台。葛川杖屦之所。台之北。临溪为亭。扁曰乐水。乐水者。处士慎权之号也。继林葛川而居于此。退溪之命名也。以葛川故林氏子孙书其事。跻葛川以配退溪。慎氏则不敢望也。后慎氏世守其居。多科宦。有力过林氏。乃曰。台我家物也。为诗而刻于台之阴。盛推其祖。以为台之主人。又刻其子孙宗族之名于其下。累累如碑碣之系者。凡守宰使客之往来。而求是台者。皆知有慎氏。而不知林氏。林氏大恚曰。此葛川杖屦之所也。彼慎何与焉。于是林慎交恶。讼之县之监司之政府。互相胜负。至今百年而不决。其间以讼死者几人。败家荡产者。大略相当。南方之士。多右林氏。然以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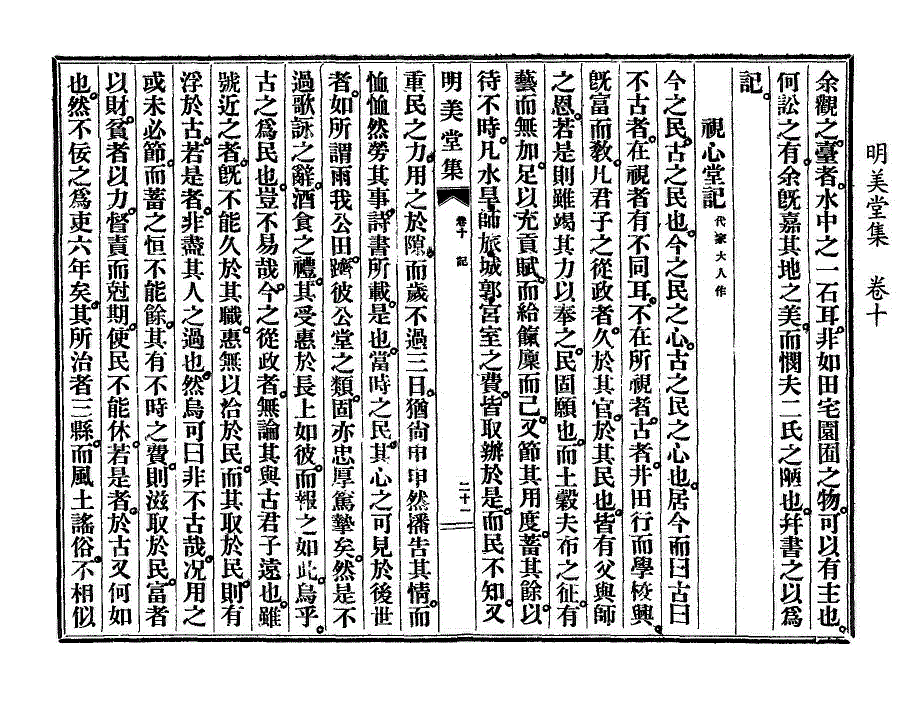 余观之。台者。水中之一石耳。非如田宅园囿之物。可以有主也。何讼之有。余既嘉其地之美。而悯夫二氏之陋也。并书之以为记。
余观之。台者。水中之一石耳。非如田宅园囿之物。可以有主也。何讼之有。余既嘉其地之美。而悯夫二氏之陋也。并书之以为记。视心堂记(代家大人作)
今之民。古之民也。今之民之心。古之民之心也。居今而曰古曰不古者。在视者有不同耳。不在所视者。古者。井田行而学校兴。既富而教。凡君子之从政者。久于其官。于其民也。皆有父与师之恩。若是则虽竭其力以奉之。民固愿也。而土谷夫布之征。有艺而无加。足以充贡赋。而给饩廪而已。又节其用度。蓄其馀。以待不时。凡水旱,师旅,城郭,宫室之费。皆取办于是。而民不知。又重民之力。用之于隙。而岁不过三日。犹尚申申然播告其情。而恤恤然劳其事。诗书所载。是也。当时之民。其心之可见于后世者。如所谓雨我公田。跻彼公堂之类。固亦忠厚笃挚矣。然是不过歌咏之辞。酒食之礼。其受惠于长上如彼。而报之如此。乌乎。古之为民也。岂不易哉。今之从政者。无论其与古君子远也。虽号近之者。既不能久于其职。惠无以洽于民。而其取于民。则有浮于古。若是者。非尽其人之过也。然乌可曰非不古哉。况用之或未必节。而蓄之恒不能馀。其有不时之费。则滋取于民。富者以财。贫者以力。督责而尅期。使民不能休。若是者。于古又何如也。然不佞之为吏六年矣。其所治者三县。而风土谣俗。不相似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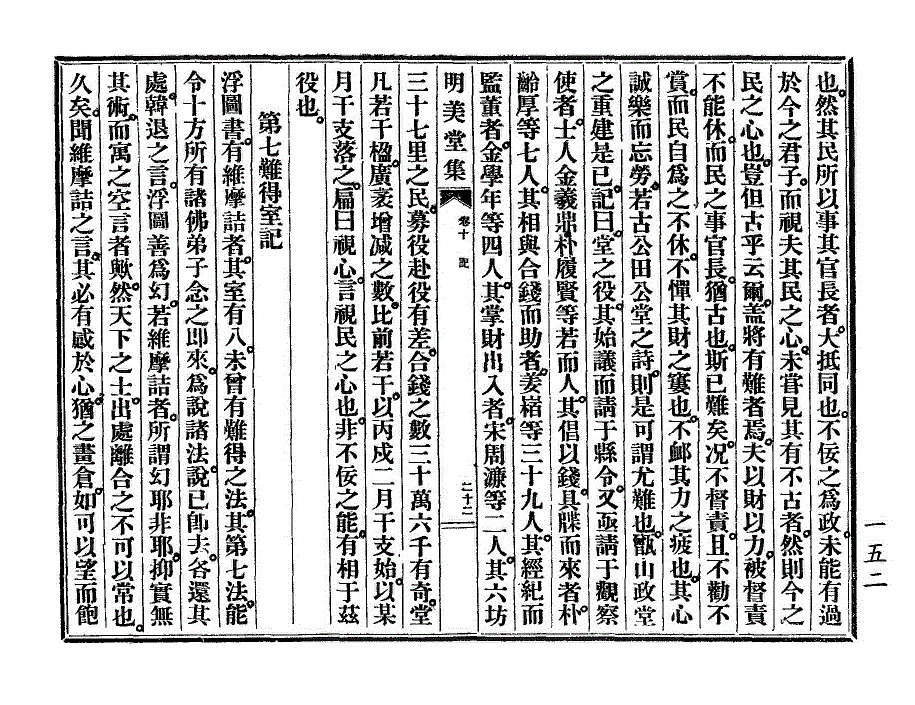 也。然其民所以事其官长者。大抵同也。不佞之为政。未能有过于今之君子。而视夫其民之心。未尝见其有不古者。然则今之民之心也。岂但古乎云尔。盖将有难者焉。夫以财以力。被督责不能休。而民之事官长。犹古也。斯已难矣。况不督责。且不劝不赏。而民自为之不休。不惮其财之窭也。不恤其力之疲也。其心诚乐而忘劳。若古公田公堂之诗。则是可谓尤难也。甑山政堂之重建是已。记曰。堂之役。其始议而请于县令。又亟请于观察使者。士人金羲鼎,朴履贤等若而人。其倡以钱。具牒而来者。朴龄厚等七人。其相与合钱而助者。姜
也。然其民所以事其官长者。大抵同也。不佞之为政。未能有过于今之君子。而视夫其民之心。未尝见其有不古者。然则今之民之心也。岂但古乎云尔。盖将有难者焉。夫以财以力。被督责不能休。而民之事官长。犹古也。斯已难矣。况不督责。且不劝不赏。而民自为之不休。不惮其财之窭也。不恤其力之疲也。其心诚乐而忘劳。若古公田公堂之诗。则是可谓尤难也。甑山政堂之重建是已。记曰。堂之役。其始议而请于县令。又亟请于观察使者。士人金羲鼎,朴履贤等若而人。其倡以钱。具牒而来者。朴龄厚等七人。其相与合钱而助者。姜第七难得室记
浮图书。有维摩诘者。其室有八。未曾有难得之法。其第七法。能令十方所有诸佛弟子念之即来。为说诸法。说已即去。各还其处。韩退之言。浮图善为幻。若维摩诘者。所谓幻耶非耶。抑实无其术。而寓之空言者欤。然天下之士。出处离合之不可以常也。久矣。闻维摩诘之言。其必有感于心。犹之画仓。如可以望而饱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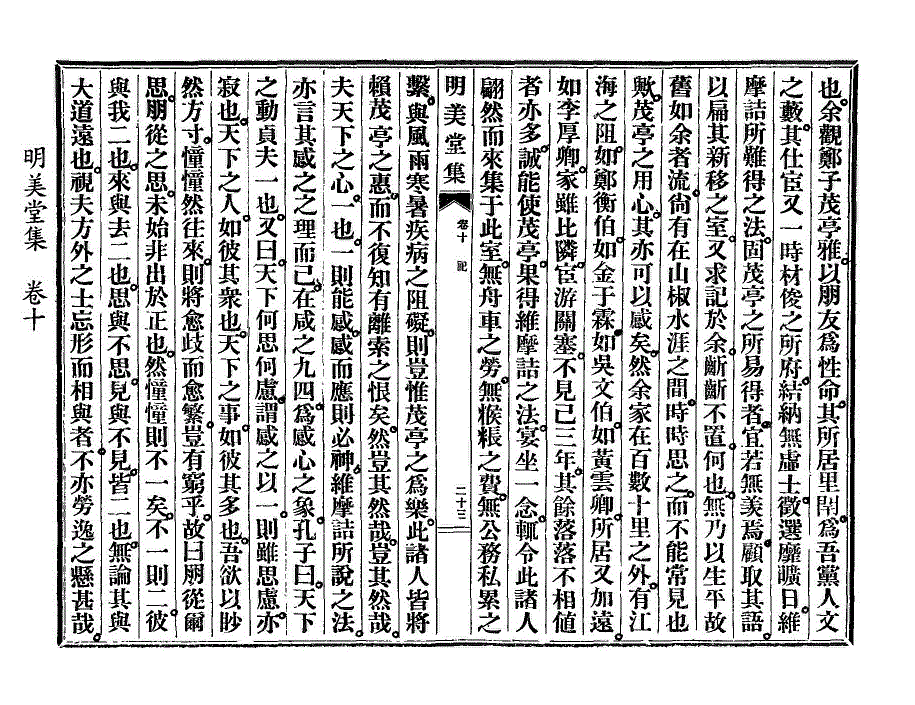 也。余观郑子茂亭雅。以朋友为性命。其所居里闬。为吾党人文之薮。其仕宦又一时材俊之所府。结纳无虚士。徵选靡旷日。维摩诘所难得之法。固茂亭之所易得者。宜若无羡焉。顾取其语。以扁其新移之室。又求记于余。龂龂不置。何也。无乃以生平故旧如余者流。尚有在山椒水涯之间。时时思之。而不能常见也欤。茂亭之用心。其亦可以感矣。然余家在百数十里之外。有江海之阻。如郑衡伯。如金于霖。如吴文伯。如黄云卿。所居又加远。如李厚卿。家虽比邻。宦游关塞。不见已三年。其馀落落不相值者亦多。诚能使茂亭。果得维摩诘之法。宴坐一念。辄令此诸人翩然而来集于此室。无舟车之劳。无糇粻之费。无公务私累之系。与风雨寒暑疾病之阻碍。则岂惟茂亭之为乐。此诸人皆将赖茂亭之惠。而不复知有离索之恨矣。然岂其然哉。岂其然哉。夫天下之心。一也。一则能感。感而应则必神。维摩诘所说之法。亦言其感之之理而已。在咸之九四。为感心之象。孔子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天下何思何虑。谓感之以一。则虽思虑。亦寂也。天下之人。如彼其众也。天下之事。如彼其多也。吾欲以眇然方寸。憧憧然往来。则将愈歧而愈繁。岂有穷乎。故曰朋从尔思。朋从之思。未始非出于正也。然憧憧则不一矣。不一则二。彼与我二也。来与去二也。思与不思。见与不见。皆二也。无论其与大道远也。视夫方外之士忘形而相与者。不亦劳逸之悬甚哉。
也。余观郑子茂亭雅。以朋友为性命。其所居里闬。为吾党人文之薮。其仕宦又一时材俊之所府。结纳无虚士。徵选靡旷日。维摩诘所难得之法。固茂亭之所易得者。宜若无羡焉。顾取其语。以扁其新移之室。又求记于余。龂龂不置。何也。无乃以生平故旧如余者流。尚有在山椒水涯之间。时时思之。而不能常见也欤。茂亭之用心。其亦可以感矣。然余家在百数十里之外。有江海之阻。如郑衡伯。如金于霖。如吴文伯。如黄云卿。所居又加远。如李厚卿。家虽比邻。宦游关塞。不见已三年。其馀落落不相值者亦多。诚能使茂亭。果得维摩诘之法。宴坐一念。辄令此诸人翩然而来集于此室。无舟车之劳。无糇粻之费。无公务私累之系。与风雨寒暑疾病之阻碍。则岂惟茂亭之为乐。此诸人皆将赖茂亭之惠。而不复知有离索之恨矣。然岂其然哉。岂其然哉。夫天下之心。一也。一则能感。感而应则必神。维摩诘所说之法。亦言其感之之理而已。在咸之九四。为感心之象。孔子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天下何思何虑。谓感之以一。则虽思虑。亦寂也。天下之人。如彼其众也。天下之事。如彼其多也。吾欲以眇然方寸。憧憧然往来。则将愈歧而愈繁。岂有穷乎。故曰朋从尔思。朋从之思。未始非出于正也。然憧憧则不一矣。不一则二。彼与我二也。来与去二也。思与不思。见与不见。皆二也。无论其与大道远也。视夫方外之士忘形而相与者。不亦劳逸之悬甚哉。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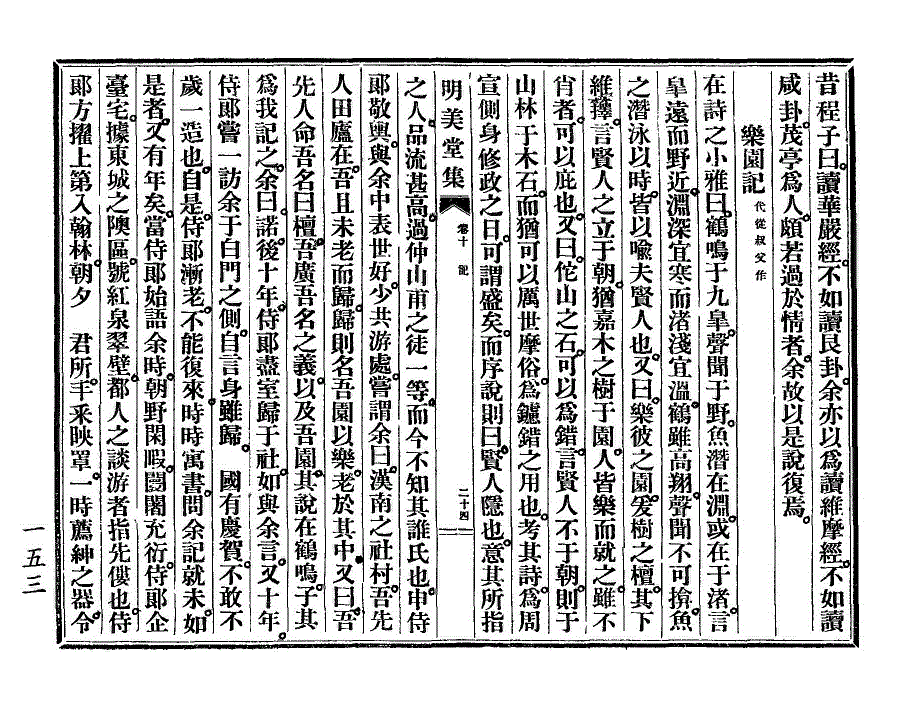 昔程子曰。读华严经。不如读艮卦。余亦以为读维摩经。不如读咸卦。茂亭为人。颇若过于情者。余故以是说复焉。
昔程子曰。读华严经。不如读艮卦。余亦以为读维摩经。不如读咸卦。茂亭为人。颇若过于情者。余故以是说复焉。乐园记(代从叔父作)
在诗之小雅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言皋远而野近。渊深宜寒而渚浅宜温。鹤虽高翔。声闻不可掩。鱼之潜泳以时。皆以喻夫贤人也。又曰。乐彼之园。爰树之檀。其下维萚。言贤人之立于朝。犹嘉木之树于园。人皆乐而就之。虽不肖者。可以庇也。又曰。佗山之石。可以为错。言贤人不于朝。则于山林于木石。而犹可以厉世摩俗。为铝错之用也。考其诗。为周宣侧身修政之日。可谓盛矣。而序说则曰。贤人隐也。意其所指之人。品流甚高。过仲山甫之徒一等。而今不知其谁氏也。申侍郎敬舆。与余中表世好。少共游处。尝谓余曰。汉南之社村。吾先人田庐在。吾且未老而归。归则名吾园以乐。老于其中。又曰。吾先人命吾名曰檀。吾广吾名之义。以及吾园。其说在鹤鸣。子其为我记之。余曰。诺。后十年。侍郎尽室归于社。如与余言。又十年。侍郎尝一访余于白门之侧。自言身虽归。 国有庆贺。不敢不岁一造也。自是。侍郎渐老。不能复来。时时寓书。问余记就未。如是者。又有年矣。当侍郎始语余时。朝野闲暇。阛阇充衍。侍郎企台宅。据东城之隩区。号红泉翠壁。都人之谈游者指先偻也。侍郎方擢上第入翰林。朝夕 君所。丰采映罩。一时荐绅之器。令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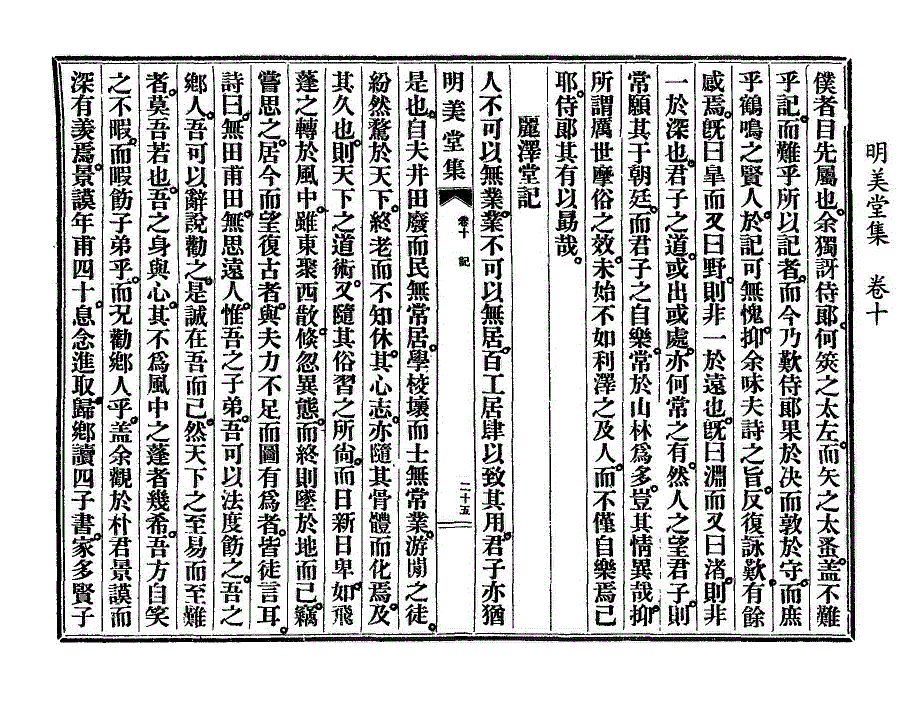 仆者目先属也。余独讶侍郎。何筴之太左。而矢之太蚤。盖不难乎记。而难乎所以记者。而今乃叹侍郎果于决而敦于守。而庶乎鹤鸣之贤人。于记可无愧。抑余味夫诗之旨。反复咏叹。有馀感焉。既曰皋而又曰野。则非一于远也。既曰渊而又曰渚。则非一于深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亦何常之有。然人之望君子。则常愿其于朝廷。而君子之自乐。常于山林为多。岂其情异哉。抑所谓厉世摩俗之效。未始不如利泽之及人。而不仅自乐焉已耶。侍郎其有以勖哉。
仆者目先属也。余独讶侍郎。何筴之太左。而矢之太蚤。盖不难乎记。而难乎所以记者。而今乃叹侍郎果于决而敦于守。而庶乎鹤鸣之贤人。于记可无愧。抑余味夫诗之旨。反复咏叹。有馀感焉。既曰皋而又曰野。则非一于远也。既曰渊而又曰渚。则非一于深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亦何常之有。然人之望君子。则常愿其于朝廷。而君子之自乐。常于山林为多。岂其情异哉。抑所谓厉世摩俗之效。未始不如利泽之及人。而不仅自乐焉已耶。侍郎其有以勖哉。丽泽堂记
人不可以无业。业不可以无居。百工居肆以致其用。君子亦犹是也。自夫井田废而民无常居。学校坏而士无常业。游閒之徒。纷然骛于天下。终老而不知休。其心志。亦随其骨体而化焉。及其久也。则天下之道术。又随其俗习之所尚。而日新日卑。如飞蓬之转于风中。虽东聚西散。倏忽异态。而终则坠于地而已。窃尝思之。居今而望复古者。与夫力不足而图有为者。皆徒言耳。诗曰。无田甫田。无思远人。惟吾之子弟。吾可以法度饬之。吾之乡人。吾可以辞说劝之。是诚在吾而已。然天下之至易而至难者。莫吾若也。吾之身与心。其不为风中之蓬者几希。吾方自笑之不暇。而暇饬子弟乎。而况劝乡人乎。盖余观于朴君景谟而深有羡焉。景谟年甫四十。息念进取。归乡读四子书。家多贤子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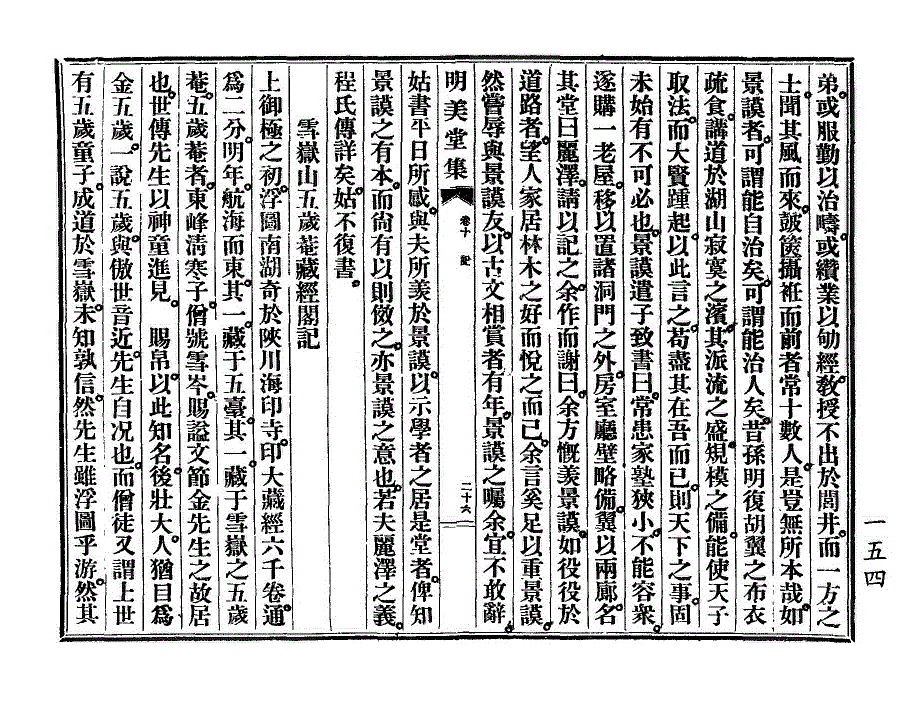 弟。或服勤以治畴。或缵业以劬经。教授不出于闾井。而一方之士。闻其风而来。鼓箧摄衽而前者常十数人。是岂无所本哉。如景谟者。可谓能自治矣。可谓能治人矣。昔孙明复胡翼之布衣疏食。讲道于湖山寂寞之滨。其派流之盛。规模之备。能使天子取法。而大贤踵起。以此言之。苟尽其在吾而已。则天下之事。固未始有不可必也。景谟遣子致书曰。常患家塾狭小。不能容众。遂购一老屋。移以置诸洞门之外。房室厅壁略备。翼以两廊。名其堂曰丽泽。请以记之。余作而谢曰。余方慨羡景谟。如役役于道路者。望人家居林木之好而悦之而已。余言奚足以重景谟。然尝辱与景谟友。以古文相赏者有年。景谟之嘱余。宜不敢辞。姑书平日所感。与夫所羡于景谟。以示学者之居是堂者。俾知景谟之有本。而尚有以则效之。亦景谟之意也。若夫丽泽之义。程氏传详矣。姑不复书。
弟。或服勤以治畴。或缵业以劬经。教授不出于闾井。而一方之士。闻其风而来。鼓箧摄衽而前者常十数人。是岂无所本哉。如景谟者。可谓能自治矣。可谓能治人矣。昔孙明复胡翼之布衣疏食。讲道于湖山寂寞之滨。其派流之盛。规模之备。能使天子取法。而大贤踵起。以此言之。苟尽其在吾而已。则天下之事。固未始有不可必也。景谟遣子致书曰。常患家塾狭小。不能容众。遂购一老屋。移以置诸洞门之外。房室厅壁略备。翼以两廊。名其堂曰丽泽。请以记之。余作而谢曰。余方慨羡景谟。如役役于道路者。望人家居林木之好而悦之而已。余言奚足以重景谟。然尝辱与景谟友。以古文相赏者有年。景谟之嘱余。宜不敢辞。姑书平日所感。与夫所羡于景谟。以示学者之居是堂者。俾知景谟之有本。而尚有以则效之。亦景谟之意也。若夫丽泽之义。程氏传详矣。姑不复书。雪岳山五岁庵藏经阁记
上御极之初。浮图南湖奇于陜川海印寺。印大藏经六千卷。通为二分。明年。航海而东。其一。藏于五台。其一。藏于雪岳之五岁庵。五岁庵者。东峰清寒子。僧号雪岑。赐谥文节金先生之故居也。世传先生以神童进见。 赐帛。以此知名。后壮大。人犹目为金五岁。一说五岁。与傲世音近。先生自况也。而僧徒又谓上世有五岁童子。成道于雪岳。未知孰信。然先生虽浮图乎游。然其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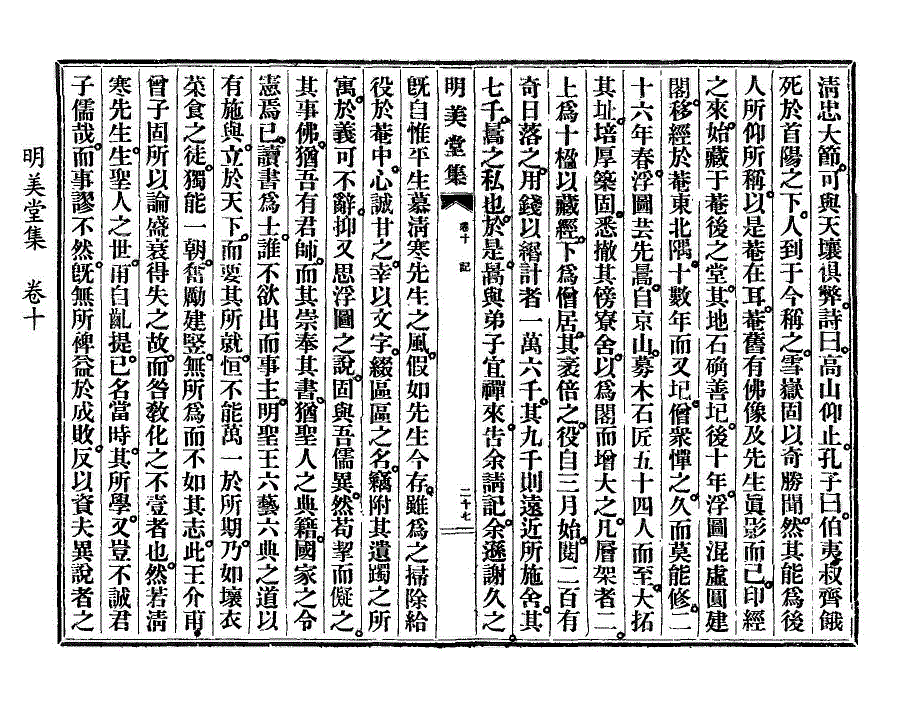 清忠大节。可与天壤俱弊。诗曰。高山仰止。孔子曰。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人到于今称之。雪岳固以奇胜闻。然其能为后人所仰所称。以是庵在耳。庵旧有佛像及先生真影而已。印经之来。始藏于庵后之堂。其地石确善圮。后十年。浮图混虚圆建阁。移经于庵东北隅。十数年而又圮。僧众惮之。久而莫能修。二十六年春。浮图芸先皓。自京山。募木石匠五十四人而至。大拓其址。培厚筑固。悉撤其傍寮舍。以为阁而增大之。凡层架者二。上为十楹以藏经。下为僧居。其袤倍之。役自三月始。阅二百有奇日落之。用钱以缗计者一万六千。其九千则远近所施舍。其七千。皓之私也。于是。皓与弟子宜禅来。告余请记。余逊谢久之。既自惟平生慕清寒先生之风。假如先生今存。虽为之扫除给役于庵中。心诚甘之。幸以文字。缀区区之名。窃附其遗躅之所寓。于义可不辞。抑又思浮图之说。固与吾儒异。然苟挈而儗之。其事佛。犹吾有君师。而其崇奉其书。犹圣人之典籍。国家之令宪焉已。读书为士。谁不欲出而事主。明圣王六艺六典之道以有施与。立于天下。而要其所就。恒不能万一于所期。乃如坏衣菜食之徒。独能一朝。奋励建竖。无所为而不如其志。此王介甫,曾子固所以论盛衰得失之故。而咎教化之不壹者也。然若清寒先生。生圣人之世。甫自龀提。已名当时。其所学。又岂不诚君子儒哉。而事谬不然。既无所裨益于成败。反以资夫异说者之
清忠大节。可与天壤俱弊。诗曰。高山仰止。孔子曰。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人到于今称之。雪岳固以奇胜闻。然其能为后人所仰所称。以是庵在耳。庵旧有佛像及先生真影而已。印经之来。始藏于庵后之堂。其地石确善圮。后十年。浮图混虚圆建阁。移经于庵东北隅。十数年而又圮。僧众惮之。久而莫能修。二十六年春。浮图芸先皓。自京山。募木石匠五十四人而至。大拓其址。培厚筑固。悉撤其傍寮舍。以为阁而增大之。凡层架者二。上为十楹以藏经。下为僧居。其袤倍之。役自三月始。阅二百有奇日落之。用钱以缗计者一万六千。其九千则远近所施舍。其七千。皓之私也。于是。皓与弟子宜禅来。告余请记。余逊谢久之。既自惟平生慕清寒先生之风。假如先生今存。虽为之扫除给役于庵中。心诚甘之。幸以文字。缀区区之名。窃附其遗躅之所寓。于义可不辞。抑又思浮图之说。固与吾儒异。然苟挈而儗之。其事佛。犹吾有君师。而其崇奉其书。犹圣人之典籍。国家之令宪焉已。读书为士。谁不欲出而事主。明圣王六艺六典之道以有施与。立于天下。而要其所就。恒不能万一于所期。乃如坏衣菜食之徒。独能一朝。奋励建竖。无所为而不如其志。此王介甫,曾子固所以论盛衰得失之故。而咎教化之不壹者也。然若清寒先生。生圣人之世。甫自龀提。已名当时。其所学。又岂不诚君子儒哉。而事谬不然。既无所裨益于成败。反以资夫异说者之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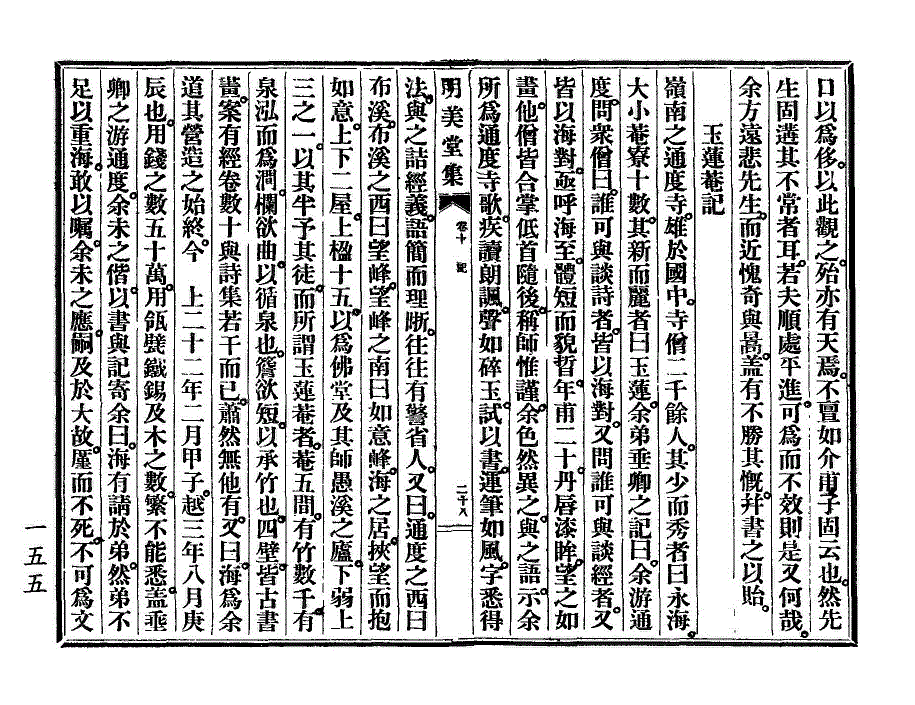 口以为侈。以此观之。殆亦有天焉。不亶如介甫,子固云也。然先生固遘其不常者耳。若夫顺处平进。可为而不效则是又何哉。余方远悲先生。而近愧奇与皓。盖有不胜其慨。并书之以贻。
口以为侈。以此观之。殆亦有天焉。不亶如介甫,子固云也。然先生固遘其不常者耳。若夫顺处平进。可为而不效则是又何哉。余方远悲先生。而近愧奇与皓。盖有不胜其慨。并书之以贻。玉莲庵记
岭南之通度寺。雄于国中。寺僧二千馀人。其少而秀者曰永海。大小庵寮十数。其新而丽者曰玉莲。余弟垂卿之记曰。余游通度。问众僧曰。谁可与谈诗者。皆以海对。又问谁可与谈经者。又皆以海对。亟呼海至。体短而貌晢(一作晰)。年甫二十。丹唇漆眸。望之如画。他僧皆合掌低首随后。称师惟谨。余色然异之。与之语。示余所为通度寺歌。疾读朗讽。声如碎玉。试以书。运笔如风。字悉得法。与之诘经义。语简而理晢。往往有警省人。又曰。通度之西曰布溪。布溪之西曰望峰。望峰之南曰如意峰。海之居。挟望而抱如意。上下二屋。上楹十五。以为佛堂及其师愚溪之庐。下弱上三之一。以其半予其徒。而所谓玉莲庵者。庵五间。有竹数千。有泉泓而为涧。栏欲曲。以循泉也。檐欲短。以承竹也。四壁。皆古书画。案有经卷数十与诗集若干而已。萧然无他有。又曰。海为余道其营造之始终。今 上二十二年二月甲子。越三年八月庚辰也。用钱之数五十万。用瓴甓铁锡及木之数。繁不能悉。盖垂卿之游通度。余未之偕。以书与记寄余曰。海有请于弟。然弟不足以重海。敢以嘱。余未之应。嗣及于大故。廑而不死。不可为文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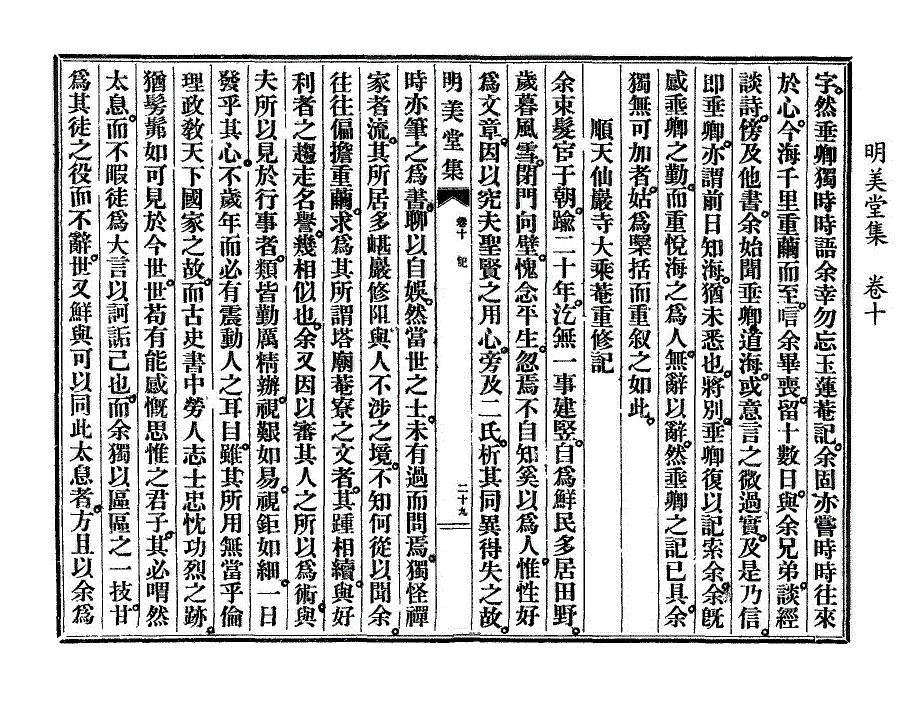 字。然垂卿独时时语余幸勿忘玉莲庵记。余固亦尝时时往来于心。今海千里重茧而至。唁余毕丧。留十数日。与余兄弟。谈经谈诗。傍及他书。余始闻垂卿,道海。或意言之微过实。及是乃信。即垂卿。亦谓前日知海。犹未悉也。将别。垂卿复以记索余。余既感垂卿之勤。而重悦海之为人。无辞以辞。然垂卿之记已具。余独无可加者。姑为檃括而重叙之如此。
字。然垂卿独时时语余幸勿忘玉莲庵记。余固亦尝时时往来于心。今海千里重茧而至。唁余毕丧。留十数日。与余兄弟。谈经谈诗。傍及他书。余始闻垂卿,道海。或意言之微过实。及是乃信。即垂卿。亦谓前日知海。犹未悉也。将别。垂卿复以记索余。余既感垂卿之勤。而重悦海之为人。无辞以辞。然垂卿之记已具。余独无可加者。姑为檃括而重叙之如此。顺天仙岩寺大乘庵重修记
余束发宦于朝。踰二十年。汔无一事建竖。自为鲜民多居田野。岁暮风雪。闭门向壁。愧念平生。忽焉不自知奚以为人。惟性好为文章。因以究夫圣贤之用心。旁及二氏。析其同异得失之故。时亦笔之为书。聊以自娱。然当世之士。未有过而问焉。独怪禅家者流。其所居多嵁岩修阻。与人不涉之境。不知何从以闻余。往往偏担重茧。求为其所谓塔庙庵寮之文者。其踵相续。与好利者之趋走名誉。几相似也。余又因以审其人之所以为术。与夫所以见于行事者。类皆勤厉精办。视艰如易。视钜如细。一日发乎其心。不岁年而必有震动人之耳目。虽其所用无当乎伦理政教天下国家之故。而古史书中劳人志士忠忱功烈之迹。犹髣髴如可见于今世。世苟有能感慨思惟之君子。其必喟然太息。而不暇徒为大言以诃诟已也。而余独以区区之一技。甘为其徒之役而不辞。世又鲜与可以同此太息者。方且以余为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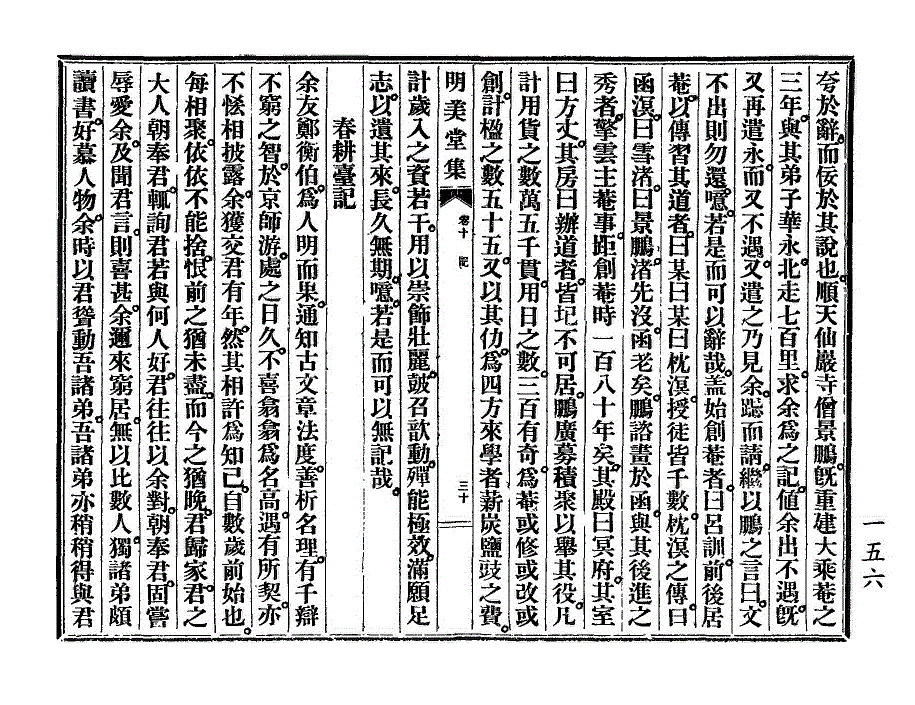 夸于辞。而佞于其说也。顺天仙岩寺僧景鹏。既重建大乘庵之三年。与其弟子华永。北走七百里。求余为之记。值余出不遇。既又再遣永。而又不遇。又遣之乃见余。跽而请。继以鹏之言曰。文不出则勿还。噫。若是而可以辞哉。盖始创庵者。曰吕训。前后居庵。以传习其道者。曰某曰某曰枕溟。授徒皆千数。枕溟之传。曰函溟。曰雪渚。曰景鹏。渚先没。函老矣。鹏咨画于函。与其后进之秀者。擎云主庵事。距创庵时一百八十年矣。其殿曰冥府。其室曰方丈。其房曰办道者。皆圮不可居。鹏广募积聚以举其役。凡计用货之数万五千贯。用日之数。三百有奇。为庵或修或改或创。计楹之数五十五。又以其仂。为四方来学者薪炭盐豉之费。计岁入之资若干。用以崇饰壮丽。鼓召歆动。殚能极效。满愿足志。以遗其来。长久无期。噫。若是而可以无记哉。
夸于辞。而佞于其说也。顺天仙岩寺僧景鹏。既重建大乘庵之三年。与其弟子华永。北走七百里。求余为之记。值余出不遇。既又再遣永。而又不遇。又遣之乃见余。跽而请。继以鹏之言曰。文不出则勿还。噫。若是而可以辞哉。盖始创庵者。曰吕训。前后居庵。以传习其道者。曰某曰某曰枕溟。授徒皆千数。枕溟之传。曰函溟。曰雪渚。曰景鹏。渚先没。函老矣。鹏咨画于函。与其后进之秀者。擎云主庵事。距创庵时一百八十年矣。其殿曰冥府。其室曰方丈。其房曰办道者。皆圮不可居。鹏广募积聚以举其役。凡计用货之数万五千贯。用日之数。三百有奇。为庵或修或改或创。计楹之数五十五。又以其仂。为四方来学者薪炭盐豉之费。计岁入之资若干。用以崇饰壮丽。鼓召歆动。殚能极效。满愿足志。以遗其来。长久无期。噫。若是而可以无记哉。春耕台记
余友郑衡伯。为人明而果。通知古文章法度。善析名理。有千辩不穷之智。于京师游。处之日久。不喜翕翕为名高。遇有所契。亦不吝相披露。余获交君有年。然其相许为知己。自数岁前始也。每相聚。依依不能舍。恨前之犹未尽。而今之犹晚。君归家。君之大人朝奉君。辄询君若与何人好。君往往以余对。朝奉君。固尝辱爱余。及闻君言。则喜甚。余迩来穷居。无以比数人。独诸弟颇读书。好慕人物。余时以君耸动吾诸弟。吾诸弟亦稍稍得与君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7H 页
 游。皆以余言为信。吾季弟有事于湖中。及归。言道中历造君家。仍拜朝奉君。朝奉君又甚爱吾弟云。始君居安城。一日。奉朝奉君之命。踰境而南。筑室于镇川。既成而悉徙。徙踰岁。安城大疠。邻里十耗其九。镇川无所苦。又久之。安城民与吏鬨。挻怒于其乡。至再而甫息。安城士大夫自是多徙者矣。而吾弟云。君居镇川。其山四周环抱中为大坪。地面微隆厚。形家所谓地晕者而君宅其中。其制朴而不陋。凡纵而为室者三。上首以奉朝奉君。中为君之子之读书之所。而君自居其下。每朝辨色。君挈其子以朝朝奉君。洒扫如仪。客至。君负墙侍。朝奉君与客语。时复问君若意云何。君则具以对。客退。诣君毕其说。朝奉君。又移坐户外听之。至辨诘。不遽解。辄排户向面笑。徐出一言以平之。无不意满。独不知客去后君父子相驩。又何状。所谈说。又何如也。吾外家在镇川。而吾弟又聓于君之里。以此多识镇川人。镇川人皆曰。君始来。相宅阙地。为窑而寝居之。日募工徒。购木石摒挡。指画精良。无少舛差。费省而役遄。世乃有如此读书人。异矣。盖余未尝至君家。不能目睹君居乡事亲及他事。独尝意之以为必可观。及闻吾弟言。君孝慈勤家状。信可贵也。又可羡也。吾弟又述其所闻曰。始君之徙。君母恭人。梦君之先祖至新宅。周视而喜曰佳哉。是不可以无号。其春耕台乎。然恭人不识字。惟辨其音。兴以告朝奉君。朝奉君曰。是必春耕台也。遂命君名其居。
游。皆以余言为信。吾季弟有事于湖中。及归。言道中历造君家。仍拜朝奉君。朝奉君又甚爱吾弟云。始君居安城。一日。奉朝奉君之命。踰境而南。筑室于镇川。既成而悉徙。徙踰岁。安城大疠。邻里十耗其九。镇川无所苦。又久之。安城民与吏鬨。挻怒于其乡。至再而甫息。安城士大夫自是多徙者矣。而吾弟云。君居镇川。其山四周环抱中为大坪。地面微隆厚。形家所谓地晕者而君宅其中。其制朴而不陋。凡纵而为室者三。上首以奉朝奉君。中为君之子之读书之所。而君自居其下。每朝辨色。君挈其子以朝朝奉君。洒扫如仪。客至。君负墙侍。朝奉君与客语。时复问君若意云何。君则具以对。客退。诣君毕其说。朝奉君。又移坐户外听之。至辨诘。不遽解。辄排户向面笑。徐出一言以平之。无不意满。独不知客去后君父子相驩。又何状。所谈说。又何如也。吾外家在镇川。而吾弟又聓于君之里。以此多识镇川人。镇川人皆曰。君始来。相宅阙地。为窑而寝居之。日募工徒。购木石摒挡。指画精良。无少舛差。费省而役遄。世乃有如此读书人。异矣。盖余未尝至君家。不能目睹君居乡事亲及他事。独尝意之以为必可观。及闻吾弟言。君孝慈勤家状。信可贵也。又可羡也。吾弟又述其所闻曰。始君之徙。君母恭人。梦君之先祖至新宅。周视而喜曰佳哉。是不可以无号。其春耕台乎。然恭人不识字。惟辨其音。兴以告朝奉君。朝奉君曰。是必春耕台也。遂命君名其居。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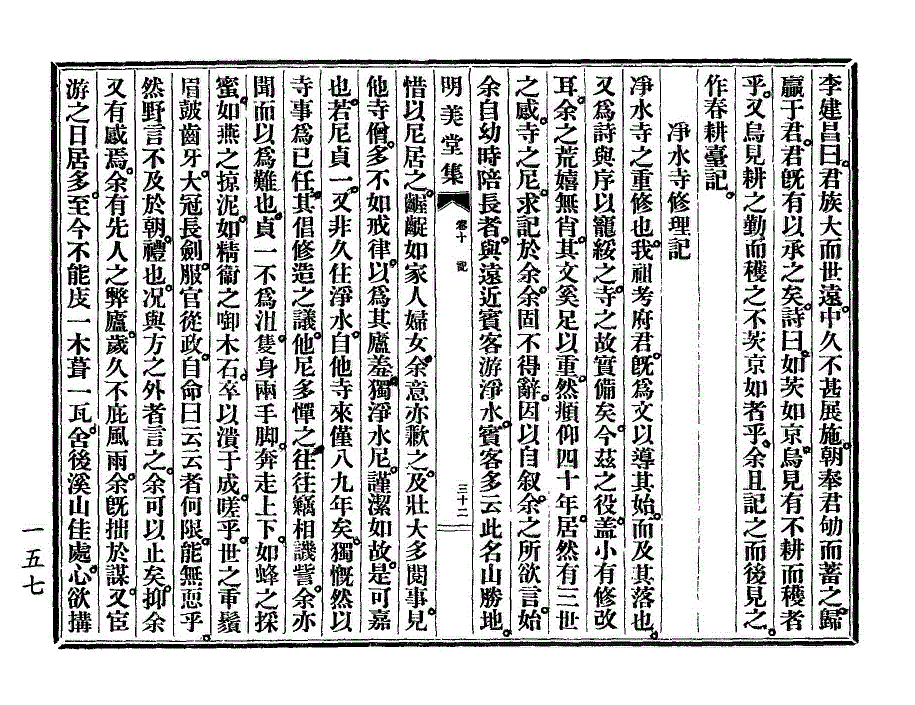 李建昌曰。君族大而世远。中久不甚展施。朝奉君劬而蓄之。归赢于君。君既有以承之矣。诗曰。如茨如京。乌见有不耕而穫者乎。又乌见耕之勤而穫之不茨京如者乎。余且记之而后见之。作春耕台记。
李建昌曰。君族大而世远。中久不甚展施。朝奉君劬而蓄之。归赢于君。君既有以承之矣。诗曰。如茨如京。乌见有不耕而穫者乎。又乌见耕之勤而穫之不茨京如者乎。余且记之而后见之。作春耕台记。净水寺修理记
净水寺之重修也。我祖考府君。既为文以导其始。而及其落也。又为诗与序以宠绥之。寺之故实备矣。今兹之役。盖小有修改耳。余之荒嬉无肖。其文奚足以重。然頫仰四十年。居然有三世之感。寺之尼。求记于余。余固不得辞。因以自叙。余之所欲言。始余自幼时陪长者。与远近宾客游净水。宾客多云此名山胜地。惜以尼居之。龌龊如家人妇女。余意亦歉之。及壮大多阅事。见他寺僧。多不如戒律。以为其庐羞。独净水尼。谨洁如故。是可嘉也。若尼贞一。又非久住净水。自他寺来仅八九年矣。独慨然以寺事为己任。其倡修造之议。他尼多惮之。往往窃相讥訾。余亦闻而以为难也。贞一不为沮。只身两手脚。奔走上下。如蜂之采蜜。如燕之掠泥。如精卫之衔木石。卒以溃于成。嗟乎。世之锸须眉鼓齿牙。大冠长剑。服官从政。自命曰云云者何限。能无恧乎。然野言不及于朝。礼也。况与方之外者言之。余可以止矣。抑余又有感焉。余有先人之弊庐。岁久不庇风雨。余既拙于谋。又宦游之日居多。至今不能庋一木葺一瓦。舍后溪山佳处。心欲搆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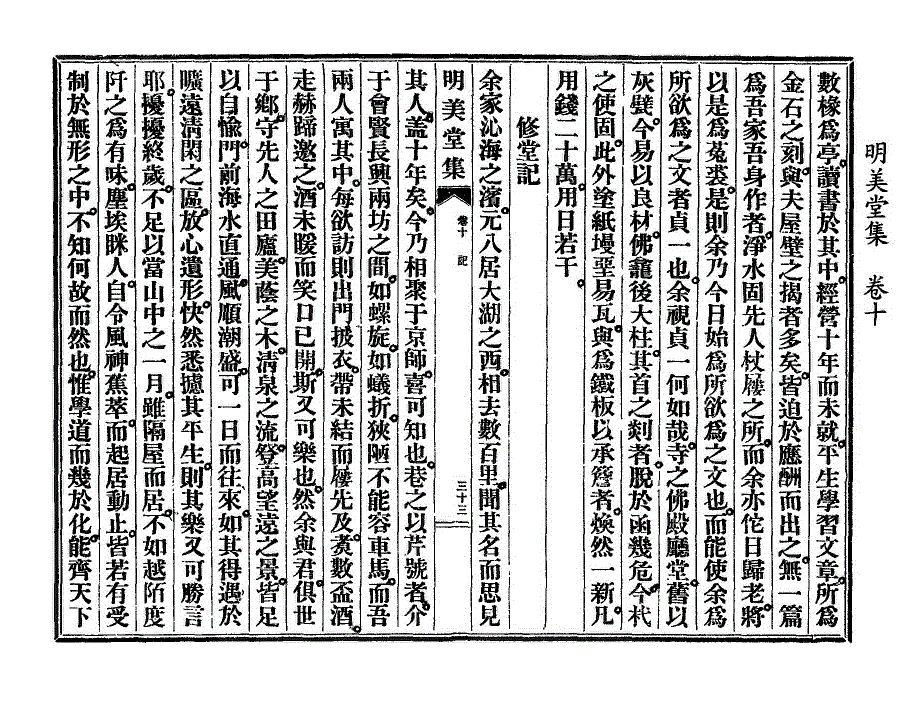 数椽为亭。读书于其中。经营十年而未就。平生学习文章。所为金石之刻。与夫屋壁之揭者多矣。皆迫于应酬而出之。无一篇为吾家吾身作者。净水固先人杖屦之所。而余亦佗日归老。将以是为菟裘。是则余乃今日始为所欲为之文也。而能使余为所欲为之文者贞一也。余视贞一何如哉。寺之佛殿厅堂。旧以灰甓。今易以良材。佛龛后大柱。其首之剡者。脱于函几危。今杙之使固。此外涂纸墁垩易瓦。与为铁板以承檐者。焕然一新。凡用钱二十万。用日若干。
数椽为亭。读书于其中。经营十年而未就。平生学习文章。所为金石之刻。与夫屋壁之揭者多矣。皆迫于应酬而出之。无一篇为吾家吾身作者。净水固先人杖屦之所。而余亦佗日归老。将以是为菟裘。是则余乃今日始为所欲为之文也。而能使余为所欲为之文者贞一也。余视贞一何如哉。寺之佛殿厅堂。旧以灰甓。今易以良材。佛龛后大柱。其首之剡者。脱于函几危。今杙之使固。此外涂纸墁垩易瓦。与为铁板以承檐者。焕然一新。凡用钱二十万。用日若干。修堂记
余家沁海之滨。元八居大湖之西。相去数百里。闻其名而思见其人。盖十年矣。今乃相聚于京师。喜可知也。巷之以芹号者。介于会贤长兴两坊之间。如螺旋。如蚁折。狭陋不能容车马。而吾两人寓其中。每欲访则出门披衣。带未结而屦先及。煮数杯酒。走赫蹄邀之。酒未暖而笑口已开。斯又可乐也。然余与君。俱世于乡。守先人之田庐。美荫之木。清泉之流。登高望远之景。皆足以自愉。门前海水直通。风顺潮盛。可一日而往来。如其得遇于旷远清闲之区。放心遗形。快然悉摅其平生。则其乐又可胜言耶。扰扰终岁。不足以当山中之一月。虽隔屋而居。不如越陌度阡之为有味。尘埃眯人。自令风神蕉萃。而起居动止。皆若有受制于无形之中。不知何故而然也。惟学道而几于化。能齐天下
明美堂集卷十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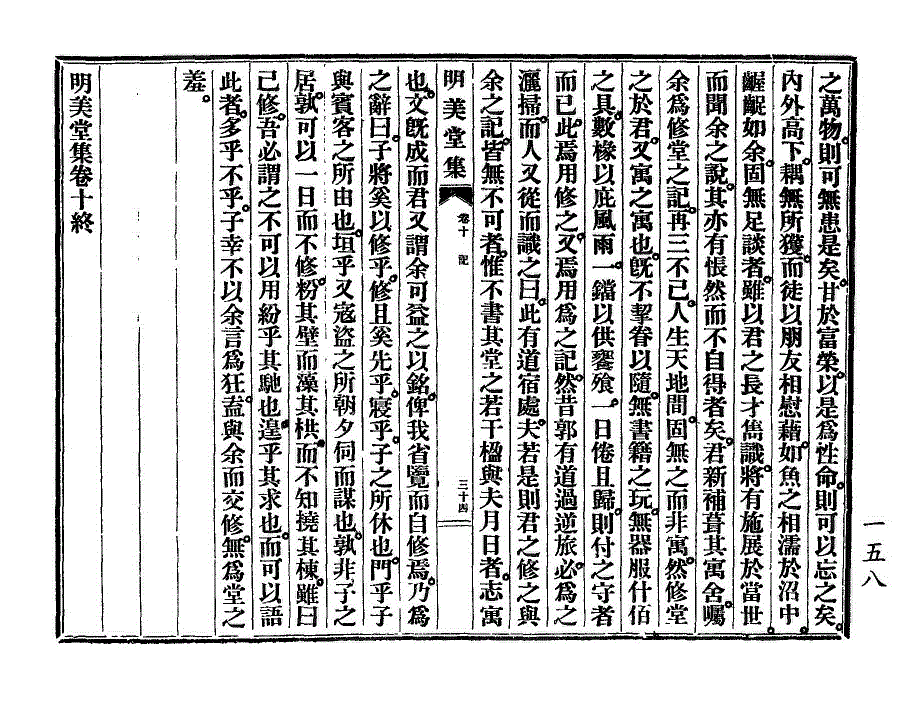 之万物。则可无患是矣。甘于富荣。以是为性命。则可以忘之矣。内外高下。耦无所获。而徒以朋友相慰藉。如鱼之相濡于沼中。龌龊如余。固无足谈者。虽以君之长才隽识。将有施展于当世。而闻余之说。其亦有怅然而不自得者矣。君新补葺其寓舍。嘱余为修堂之记。再三不已。人生天地间。固无之而非寓。然修堂之于君。又寓之寓也。既不挈眷以随。无书籍之玩。无器服什佰之具。数椽以庇风雨。一铛以供饔飧。一日倦且归。则付之守者而已。此焉用修之。又焉用为之记。然昔郭有道过逆旅。必为之洒扫。而人又从而识之曰。此有道宿处。夫若是则君之修之与余之记。皆无不可者。惟不书其堂之若干楹与夫月日者。志寓也。文既成而君又谓余可益之以铭。俾我省览而自修焉。乃为之辞曰。子将奚以修乎。修且奚先乎。寝乎。子之所休也。门乎子与宾客之所由也。垣乎又寇盗之所朝夕伺而谋也。孰非子之居。孰可以一日而不修。粉其壁而藻其栱。而不知挠其栋。虽曰已修。吾必谓之不可以用纷乎其驰也。遑乎其求也。而可以语此者。多乎不乎。子幸不以余言为狂。盍与余而交修。无为堂之羞。
之万物。则可无患是矣。甘于富荣。以是为性命。则可以忘之矣。内外高下。耦无所获。而徒以朋友相慰藉。如鱼之相濡于沼中。龌龊如余。固无足谈者。虽以君之长才隽识。将有施展于当世。而闻余之说。其亦有怅然而不自得者矣。君新补葺其寓舍。嘱余为修堂之记。再三不已。人生天地间。固无之而非寓。然修堂之于君。又寓之寓也。既不挈眷以随。无书籍之玩。无器服什佰之具。数椽以庇风雨。一铛以供饔飧。一日倦且归。则付之守者而已。此焉用修之。又焉用为之记。然昔郭有道过逆旅。必为之洒扫。而人又从而识之曰。此有道宿处。夫若是则君之修之与余之记。皆无不可者。惟不书其堂之若干楹与夫月日者。志寓也。文既成而君又谓余可益之以铭。俾我省览而自修焉。乃为之辞曰。子将奚以修乎。修且奚先乎。寝乎。子之所休也。门乎子与宾客之所由也。垣乎又寇盗之所朝夕伺而谋也。孰非子之居。孰可以一日而不修。粉其壁而藻其栱。而不知挠其栋。虽曰已修。吾必谓之不可以用纷乎其驰也。遑乎其求也。而可以语此者。多乎不乎。子幸不以余言为狂。盍与余而交修。无为堂之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