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x 页
明美堂集卷十一(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记
记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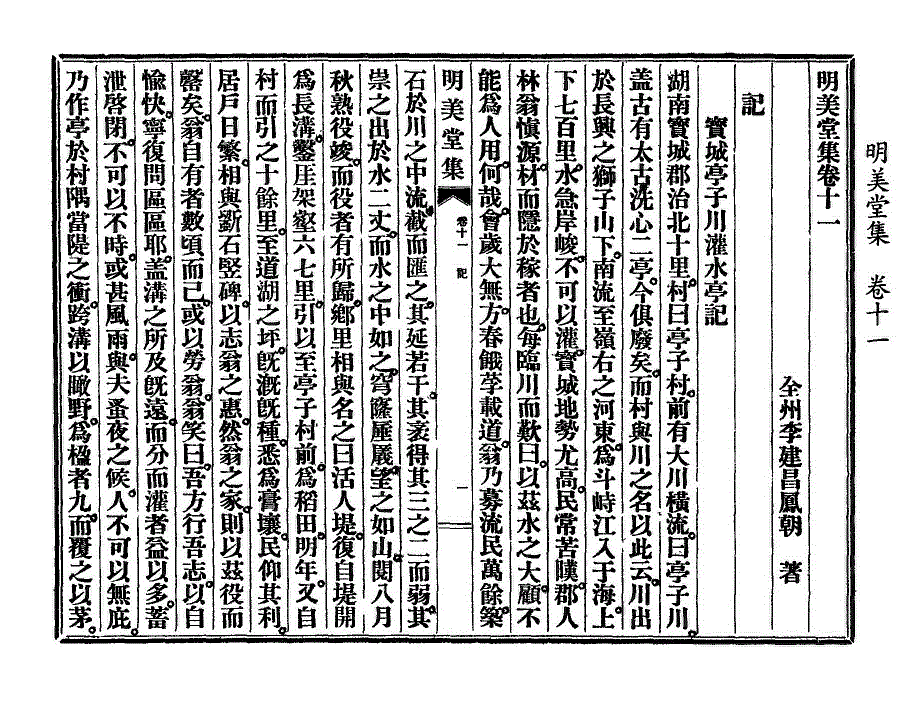 宝城亭子川灌水亭记
宝城亭子川灌水亭记湖南宝城郡治北十里。村曰亭子村。前有大川横流。曰亭子川。盖古有太古,洗心二亭。今俱废矣。而村与川之名以此云。川出于长兴之狮子山下。南流至岭右之河东。为斗峙江入于海。上下七百里。水急岸峻。不可以灌。宝城地势尤高。民常苦暵。郡人林翁慎源。材而隐于稼者也。每临川而叹曰。以兹水之大。顾不能为人用。何哉。会岁大无。方春饿莩载道。翁乃募流民万馀。筑石于川之中流。截而汇之。其延若干。其袤得其三之二而弱。其祟(一作崇)之出于水二丈。而水之中如之。穹窿厜㕒。望之如山。阅八月秋熟役竣。而役者有所归。乡里相与名之曰活人堤。复自堤开为长沟。凿厓架壑六七里。引以至亭子村前。为稻田。明年。又自村而引之十馀里。至道湖之坪。既溉既种。悉为膏壤。民仰其利。居户日繁。相与斲石竖碑。以志翁之惠。然翁之家。则以兹役而罄矣。翁自有者数顷而已。或以劳翁。翁笑曰。吾方行吾志。以自愉快。宁复问区区耶。盖沟之所及既远。而分而灌者益以多。蓄泄启闭。不可以不时。或甚风雨。与夫蚤夜之候。人不可以无庇。乃作亭于村隅当堤之冲。跨沟以瞰野。为楹者九。而覆之以茅。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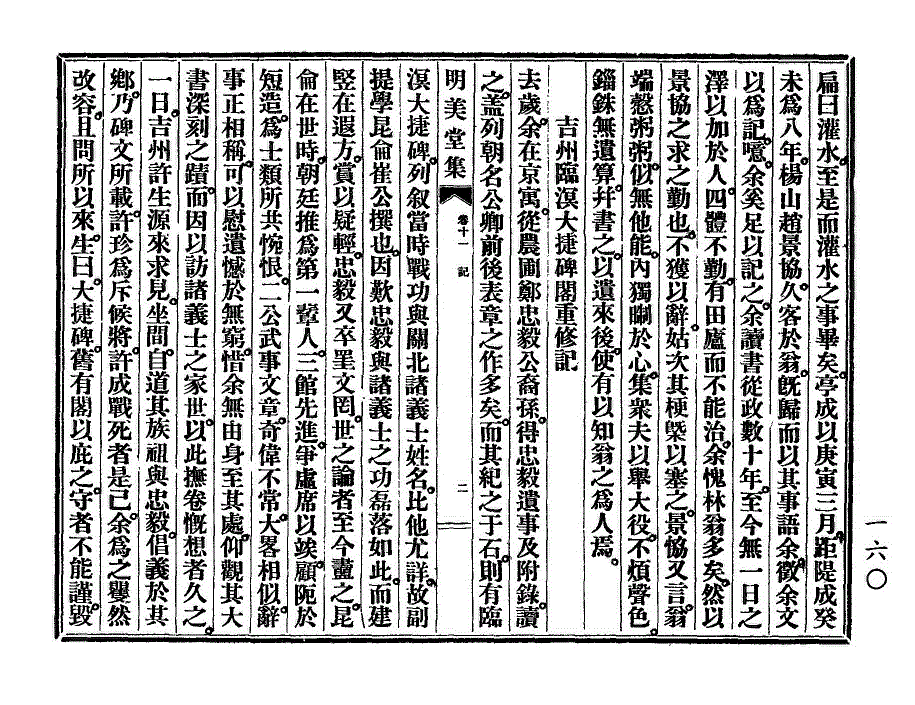 扁曰灌水。至是而灌水之事毕矣。亭成以庚寅三月。距堤成癸未为八年。杨山赵景协。久客于翁。既归而以其事语余。徵余文以为记。噫。余奚足以记之。余读书从政数十年。至今无一日之泽以加于人。四体不勤。有田庐而不能治。余愧林翁多矣。然以景协之求之勤也。不获以辞。姑次其梗槩以塞之。景恊又言。翁端悫粥粥。似无他能。内独晢于心。集众夫以举大役。不烦声色。锱铢无遗算。并书之。以遗来后。使有以知翁之为人焉。
扁曰灌水。至是而灌水之事毕矣。亭成以庚寅三月。距堤成癸未为八年。杨山赵景协。久客于翁。既归而以其事语余。徵余文以为记。噫。余奚足以记之。余读书从政数十年。至今无一日之泽以加于人。四体不勤。有田庐而不能治。余愧林翁多矣。然以景协之求之勤也。不获以辞。姑次其梗槩以塞之。景恊又言。翁端悫粥粥。似无他能。内独晢于心。集众夫以举大役。不烦声色。锱铢无遗算。并书之。以遗来后。使有以知翁之为人焉。吉州临溟大捷碑阁重修记
去岁。余在京寓。从农圃郑忠毅公裔孙。得忠毅遗事及附录。读之。盖列朝名公卿前后表章之作多矣。而其纪之于石。则有临溟大捷碑。列叙当时战功与关北诸义士姓名。比他尤详。故副提学昆仑崔公撰也。因叹忠毅与诸义士之功磊落如此。而建竖在遐方。赏以疑轻。忠毅又卒挂文罔。世之论者至今衋之。昆仑在世时。朝廷推为第一辈人。三馆先进。争虚席以俟。顾阨于短造。为士类所共惋恨。二公武事文章。奇伟不常。大略相似。辞事正相称。可以慰遗憾于无穷。惜余无由身至其处。仰观其大书深刻之迹。而因以访诸义士之家世。以此抚卷慨想者久之。一日。吉州许生源来求见。坐间。自道其族祖与忠毅。倡义于其乡。乃碑文所载。许珍为斥候将。许成战死者是已。余为之矍然改容。且问所以来。生曰。大捷碑。旧有阁以庇之。守者不能谨。毁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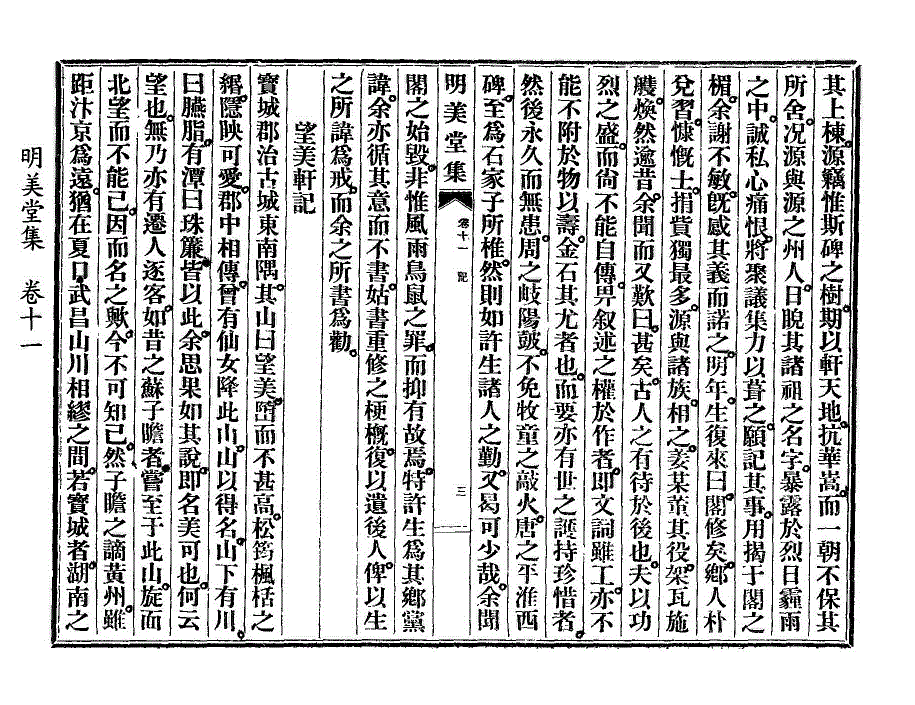 其上栋。源窃惟斯碑之树。期以轩天地。抗华嵩。而一朝不保其所舍。况源与源之州人。日睨其诸祖之名字。暴露于烈日霾雨之中。诚私心痛恨。将聚议集力以葺之。愿记其事。用揭于阁之楣。余谢不敏。既感其义而诺之。明年。生复来曰。阁修矣。乡人朴兑习。慷慨士。捐赀独最多。源与诸族。相之。姜某董其役。架瓦施艧。焕然逾昔。余闻而又叹曰。甚矣。古人之有待于后也。夫以功烈之盛。而尚不能自传。畀叙述之权于作者。即文词虽工。亦不能不附于物以寿。金石其尤者也。而要亦有世之护持珍惜者。然后永久而无患。周之岐阳鼓。不免牧童之敲火。唐之平淮西碑。至为石家子所椎。然则如许生诸人之勤。又曷可少哉。余闻阁之始毁。非惟风雨鸟鼠之罪。而抑有故焉。特许生为其乡党讳。余亦循其意而不书。姑书重修之梗概。复以遗后人。俾以生之所讳为戒。而余之所书为劝。
其上栋。源窃惟斯碑之树。期以轩天地。抗华嵩。而一朝不保其所舍。况源与源之州人。日睨其诸祖之名字。暴露于烈日霾雨之中。诚私心痛恨。将聚议集力以葺之。愿记其事。用揭于阁之楣。余谢不敏。既感其义而诺之。明年。生复来曰。阁修矣。乡人朴兑习。慷慨士。捐赀独最多。源与诸族。相之。姜某董其役。架瓦施艧。焕然逾昔。余闻而又叹曰。甚矣。古人之有待于后也。夫以功烈之盛。而尚不能自传。畀叙述之权于作者。即文词虽工。亦不能不附于物以寿。金石其尤者也。而要亦有世之护持珍惜者。然后永久而无患。周之岐阳鼓。不免牧童之敲火。唐之平淮西碑。至为石家子所椎。然则如许生诸人之勤。又曷可少哉。余闻阁之始毁。非惟风雨鸟鼠之罪。而抑有故焉。特许生为其乡党讳。余亦循其意而不书。姑书重修之梗概。复以遗后人。俾以生之所讳为戒。而余之所书为劝。望美轩记
宝城郡治古城东南隅。其山曰望美。嶞而不甚高。松筠枫栝之缗。隐映可爱。郡中相传。曾有仙女降此山。山以得名。山下有川。曰胭脂。有潭曰珠帘。皆以此。余思果如其说。即名美可也。何云望也。无乃亦有迁人逐客。如昔之苏子瞻者。尝至于此山。旋而北望而不能已。因而名之欤。今不可知已。然子瞻之谪黄州。虽距汴京为远。犹在夏口,武昌山川相缪之间。若宝城者。湖南之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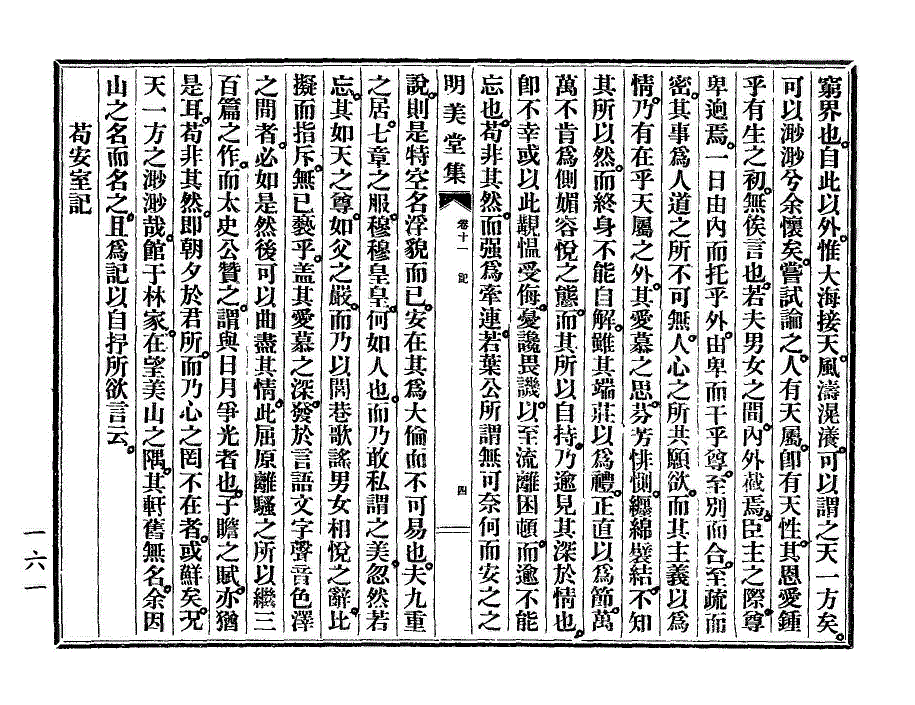 穷界也。自此以外。惟大海接天。风涛滉瀁。可以谓之天一方矣。可以渺渺兮余怀矣。尝试论之。人有天属。即有天性。其恩爱钟乎有生之初。无俟言也。若夫男女之间。内外截焉。臣主之际。尊卑迥焉。一日由内而托乎外。由卑而干乎尊。至别而合。至疏而密。其事为人道之所不可无。人心之所共愿欲。而其主义以为情。乃有在乎天属之外。其爱慕之思。芬芳悱恻。缠绵襞结。不知其所以然。而终身不能自解。虽其端庄以为礼。正直以为节。万万不肯为侧媚容悦之态。而其所以自持。乃逾见其深于情也。即不幸或以此觏愠受侮。忧谗畏讥。以至流离困顿。而逾不能忘也。苟非其然。而强为牵连。若叶公所谓无可奈何而安之之说。则是特空名浮貌而已。安在其为大伦而不可易也。夫九重之居。七章之服。穆穆皇皇。何如人也。而乃敢私谓之美。忽然若忘。其如天之尊。如父之严。而乃以闾巷歌谣男女相悦之辞。比拟而指斥。无已亵乎。盖其爱慕之深。发于言语文字声音色泽之间者。必如是然后可以曲尽其情。此屈原离骚之所以继三百篇之作。而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者也。子瞻之赋。亦犹是耳。苟非其然。即朝夕于君所。而乃心之罔不在者。或鲜矣。况天一方之渺渺哉。馆于林家。在望美山之隅。其轩旧无名。余因山之名而名之。且为记以自抒所欲言云。
穷界也。自此以外。惟大海接天。风涛滉瀁。可以谓之天一方矣。可以渺渺兮余怀矣。尝试论之。人有天属。即有天性。其恩爱钟乎有生之初。无俟言也。若夫男女之间。内外截焉。臣主之际。尊卑迥焉。一日由内而托乎外。由卑而干乎尊。至别而合。至疏而密。其事为人道之所不可无。人心之所共愿欲。而其主义以为情。乃有在乎天属之外。其爱慕之思。芬芳悱恻。缠绵襞结。不知其所以然。而终身不能自解。虽其端庄以为礼。正直以为节。万万不肯为侧媚容悦之态。而其所以自持。乃逾见其深于情也。即不幸或以此觏愠受侮。忧谗畏讥。以至流离困顿。而逾不能忘也。苟非其然。而强为牵连。若叶公所谓无可奈何而安之之说。则是特空名浮貌而已。安在其为大伦而不可易也。夫九重之居。七章之服。穆穆皇皇。何如人也。而乃敢私谓之美。忽然若忘。其如天之尊。如父之严。而乃以闾巷歌谣男女相悦之辞。比拟而指斥。无已亵乎。盖其爱慕之深。发于言语文字声音色泽之间者。必如是然后可以曲尽其情。此屈原离骚之所以继三百篇之作。而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者也。子瞻之赋。亦犹是耳。苟非其然。即朝夕于君所。而乃心之罔不在者。或鲜矣。况天一方之渺渺哉。馆于林家。在望美山之隅。其轩旧无名。余因山之名而名之。且为记以自抒所欲言云。苟安室记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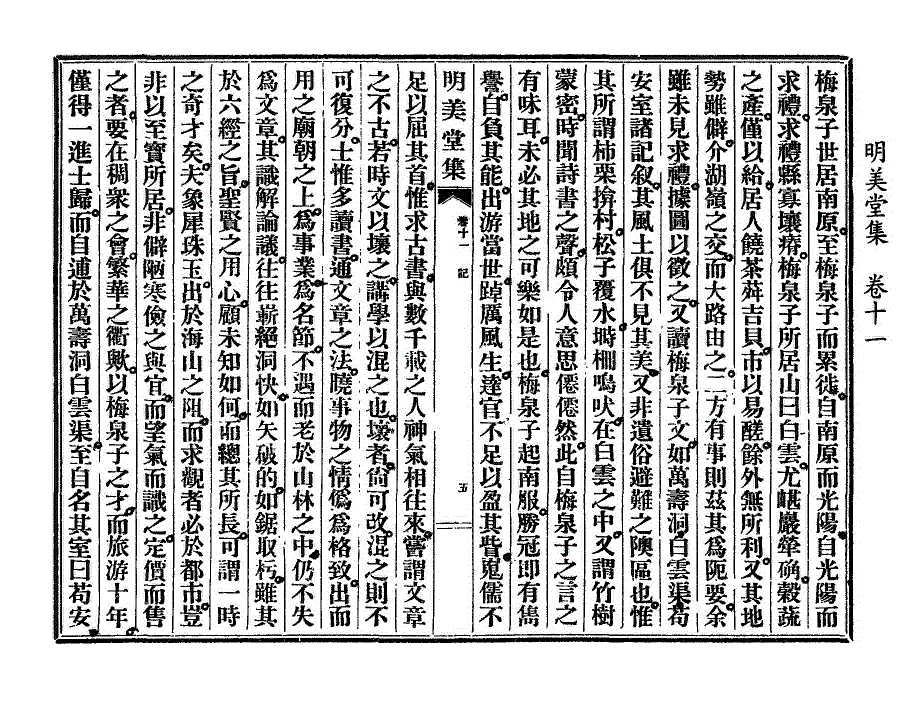 梅泉子世居南原。至梅泉子而累徙。自南原而光阳。自光阳而求礼。求礼县寡壤瘠。梅泉子所居山曰白云。尤嵁岩荦确。谷蔬之产。仅以给。居人饶茶荈吉贝。市以易醝。馀外无所利。又其地势虽僻。介湖岭之交。而大路由之。二方有事则兹其为阨要。余虽未见求礼。据图以徵之。又读梅泉子文。如万寿洞,白云渠,苟安室诸记叙。其风土俱不见其美。又非遗俗避难之隩区也。惟其所谓柿栗掩村。松子覆水。埘栅鸣吠。在白云之中。又谓竹树蒙密。时闻诗书之声。颇令人意思仙仙然。此自梅泉子之言之有味耳。未必其地之可乐如是也。梅泉子起南服。胜冠即有隽誉。自负其能。出游当世。踔厉风生。达官不足以盈其眦。嵬儒不足以屈其首。惟求古书。与数千载之人神气相往来。尝谓文章之不古。若时文以坏之。讲学以混之也。坏者。尚可改。混之则不可复分。士惟多读书。通文章之法。晓事物之情伪为格致。出而用之庙朝之上。为事业。为名节。不遇而老于山林之中。仍不失为文章。其识解论议。往往崭绝洞快。如矢破的。如锯取朽。虽其于六经之旨。圣贤之用心。顾未知如何。而总其所长。可谓一时之奇才矣。夫象犀珠玉。出于海山之阻。而求观者必于都市。岂非以至宝所居。非僻陋寒俭之与宜。而望气而识之。定价而售之者。要在稠众之会。繁华之衢欤。以梅泉子之才。而旅游十年。仅得一进士归。而自逋于万寿洞白云渠。至自名其室曰苟安。
梅泉子世居南原。至梅泉子而累徙。自南原而光阳。自光阳而求礼。求礼县寡壤瘠。梅泉子所居山曰白云。尤嵁岩荦确。谷蔬之产。仅以给。居人饶茶荈吉贝。市以易醝。馀外无所利。又其地势虽僻。介湖岭之交。而大路由之。二方有事则兹其为阨要。余虽未见求礼。据图以徵之。又读梅泉子文。如万寿洞,白云渠,苟安室诸记叙。其风土俱不见其美。又非遗俗避难之隩区也。惟其所谓柿栗掩村。松子覆水。埘栅鸣吠。在白云之中。又谓竹树蒙密。时闻诗书之声。颇令人意思仙仙然。此自梅泉子之言之有味耳。未必其地之可乐如是也。梅泉子起南服。胜冠即有隽誉。自负其能。出游当世。踔厉风生。达官不足以盈其眦。嵬儒不足以屈其首。惟求古书。与数千载之人神气相往来。尝谓文章之不古。若时文以坏之。讲学以混之也。坏者。尚可改。混之则不可复分。士惟多读书。通文章之法。晓事物之情伪为格致。出而用之庙朝之上。为事业。为名节。不遇而老于山林之中。仍不失为文章。其识解论议。往往崭绝洞快。如矢破的。如锯取朽。虽其于六经之旨。圣贤之用心。顾未知如何。而总其所长。可谓一时之奇才矣。夫象犀珠玉。出于海山之阻。而求观者必于都市。岂非以至宝所居。非僻陋寒俭之与宜。而望气而识之。定价而售之者。要在稠众之会。繁华之衢欤。以梅泉子之才。而旅游十年。仅得一进士归。而自逋于万寿洞白云渠。至自名其室曰苟安。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2L 页
 则吾恐朝廷宰相。不能无任其责。而即如余辈。欧阳公所谓无资攘臂之闲民。犹不能不怅然而失图。诚不愿梅泉子之苟安于此室也。梅泉子求余复记其室。余为叙所感者以应之。亦淮南小山之馀意云尔。
则吾恐朝廷宰相。不能无任其责。而即如余辈。欧阳公所谓无资攘臂之闲民。犹不能不怅然而失图。诚不愿梅泉子之苟安于此室也。梅泉子求余复记其室。余为叙所感者以应之。亦淮南小山之馀意云尔。质斋记
李君伯曾访余于贝州。余与伯曾别数十年矣。相见甚喜。是日余又闻赦。欣然无幽忧之怀。春雨濛濛。竟夕相与从容为欢笑。间则发其箧。得诗古文数篇。读之又甚乐。伯曾忽改容曰。吾久游于外。求薄少为老母养。苦不能满。吾将归矣。吾且去文而就质。韬踪匿影于万山之中。泯然以忘吾穷也。吾故以质名吾斋。子盍为之记。余闻之。不觉怅然有惜心焉。使伯曾之言果信也。吾不知何时。复见伯曾。纵见之。伯曾之文去矣。吾何所读而乐之。如今日也。伯曾之文。锦绣也。使为锦绣者。一朝易其机杼而为布帛。则吾不知其为利孰多。而其不足于观者之目。则有间矣。余方为伯曾惜。伯曾之自视。又乌能无情乎。虽然。微独伯曾耳。虽余之拙陋。幸而操其艺术。以自骋其区区之名。不为不久。而年岁之所迁。人事之所更。居然不能无今昔之异。而况伯曾乎。昔子贡对棘子成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其言若甚详。而吾尝读之。犹未能晓然于心。今伯曾既已自择于去就之分而无所吝。其必有以知之矣。吾又何足以为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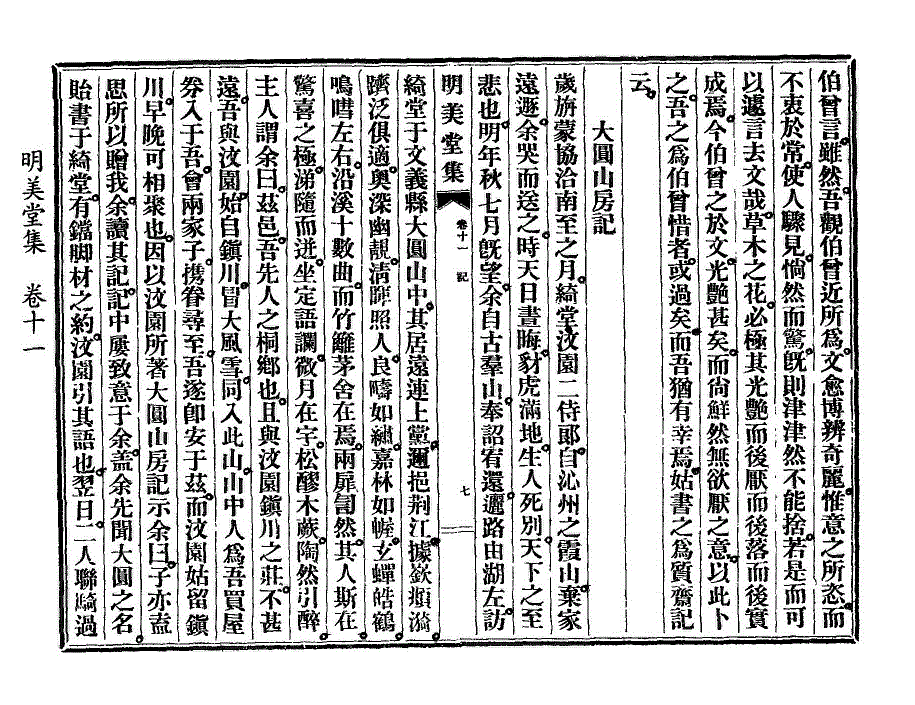 伯曾言。虽然。吾观伯曾近所为。文愈博辨奇丽。惟意之所恣。而不衷于常。使人骤见。惝然而惊。既则津津然不能舍。若是而可以遽言去文哉。草木之花。必极其光艳而后厌而后落而后实成焉。今伯曾之于文。光艳甚矣。而尚鲜然无欲厌之意。以此卜之。吾之为伯曾惜者。或过矣。而吾犹有幸焉。姑书之为质斋记云。
伯曾言。虽然。吾观伯曾近所为。文愈博辨奇丽。惟意之所恣。而不衷于常。使人骤见。惝然而惊。既则津津然不能舍。若是而可以遽言去文哉。草木之花。必极其光艳而后厌而后落而后实成焉。今伯曾之于文。光艳甚矣。而尚鲜然无欲厌之意。以此卜之。吾之为伯曾惜者。或过矣。而吾犹有幸焉。姑书之为质斋记云。大圆山房记
岁旃蒙协洽南至之月。绮堂,汶园二侍郎。自沁州之霞山。弃家远遁。余哭而送之。时天日昼晦。豺虎满地。生人死别。天下之至悲也。明年秋七月既望。余自古群山。奉诏宥还。逦路由湖左。访绮堂于文义县大圆山中。其居远连上党。迩挹荆江。据嵚頫漪。跻泛俱适。奥深幽靓。清晖照人。良畴如绣。嘉林如幄。玄蝉皓鹤。鸣嘒左右。沿溪十数曲。而竹篱茅舍在焉。两扉訇然。其人斯在。惊喜之极。涕随而迸。坐定语谰。微月在宇。松醪木蕨。陶然引醉。主人谓余曰。兹邑。吾先人之桐乡也。且与汶园镇川之庄。不甚远。吾与汶园。始自镇川。冒大风雪。同入此山。山中人为吾买屋券入于吾。会两家子。携眷寻至。吾遂即安于兹。而汶园姑留镇川。早晚可相聚也。因以汶园所著大圆山房记示余曰。子亦盍思所以赠我。余读其记。记中屡致意于余。盖余先闻大圆之名。贻书于绮堂。有铛脚材之约。汶园引其语也。翌日。二人联骑过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3L 页
 镇川。信宿于汶园宅。绮堂复申其嘱。嗟乎吾侪霞山别时。殆以为不可复见也。赖天之灵。暨 圣主之恩。得以含生戴发。相视一笑。于吾三人。则可谓幸矣。顾今乱党虽溃。矫令虽寝。而 君父危于孤注。宗国罔知税驾。哀痛愤懑。日甚月亟。其如余之辜 恩亏义。自甘为僇民弃物者。固无论耳。虽以二君之超然高蹈。身在荣辱之外者。苟以古之劳臣。若卫宁俞,鲁子家羁之事责之。其亦有蹙然而不自安于中矣。诗曰。寔命不犹。命之不犹。虽欲执羁靮以从。其势有不可得。遑敢望其裨补于万一乎。后世有原情恕迹之君子。其犹不以遗 君议其后。则吾侪可以知免。若夫汶园所云剥尽复生。大圆之有日。则固亦善颂之昌辞。而非今之所敢必也。虽然。吾三人离合悲欢之间。亦有以见天道人事纷纶错迕若是其不齐也。又不知自兹以往。将使圆者缺乎。缺者圆乎。抑果如汶园之说。而大圆有日乎。姑以所感者书之。为大圆山房第二记。
镇川。信宿于汶园宅。绮堂复申其嘱。嗟乎吾侪霞山别时。殆以为不可复见也。赖天之灵。暨 圣主之恩。得以含生戴发。相视一笑。于吾三人。则可谓幸矣。顾今乱党虽溃。矫令虽寝。而 君父危于孤注。宗国罔知税驾。哀痛愤懑。日甚月亟。其如余之辜 恩亏义。自甘为僇民弃物者。固无论耳。虽以二君之超然高蹈。身在荣辱之外者。苟以古之劳臣。若卫宁俞,鲁子家羁之事责之。其亦有蹙然而不自安于中矣。诗曰。寔命不犹。命之不犹。虽欲执羁靮以从。其势有不可得。遑敢望其裨补于万一乎。后世有原情恕迹之君子。其犹不以遗 君议其后。则吾侪可以知免。若夫汶园所云剥尽复生。大圆之有日。则固亦善颂之昌辞。而非今之所敢必也。虽然。吾三人离合悲欢之间。亦有以见天道人事纷纶错迕若是其不齐也。又不知自兹以往。将使圆者缺乎。缺者圆乎。抑果如汶园之说。而大圆有日乎。姑以所感者书之。为大圆山房第二记。普门寺大钟功德板记
青羊之岁。黄钟之月。余乃窜身荒谷。托于普门之僧舍。范蔚宗蔡伯喈赞。仰日月而不烛。临风尘而不过。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者。一段情景。约略相似。每见居僧正三,裕华辈于佛前。焚香膜拜。晨夕熏修。经声琅琅然。梵声浩浩然。军持隐囊。既饱而嬉。心甚羡之。偶问若方寸中。亦有事乎否。二僧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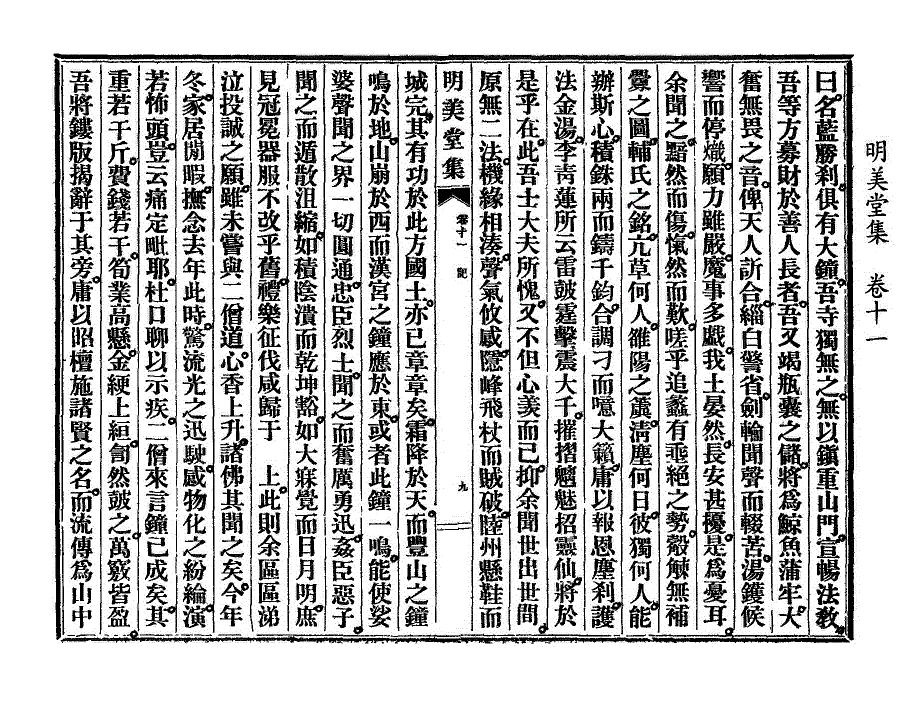 曰。名蓝胜刹。俱有大钟。吾寺独无之。无以镇重山门。宣畅法教。吾等方募财于善人长者。吾又竭瓶囊之储。将为鲸鱼蒲牢。大奋无畏之音。俾天人䜣合。缁白警省。剑轮闻声而辍苦。汤镬候响而停炽。愿力虽严。魔事多戏。我土晏然。长安甚扰。是为忧耳。余闻之。黯然而伤。忾然而叹。嗟乎追蠡有垂绝之势。觳觫无补衅之图。辅氏之铭。亢草何人。雒阳之簴。清尘何日。彼独何人。能办斯心。积铢两而铸千钧。合调刁而噫大籁。庸以报恩尘刹。护法金汤。李青莲所云雷鼓霆击震大千。摧摺魑魅招灵仙。将于是乎在。此吾士大夫所愧。又不但心羡而已。抑余闻世出世间。原无二法。机缘相凑。声气攸感。隐峰飞杖而贼破。睦州悬鞋而城完。其有功于此方国土。亦已章章矣。霜降于天。而丰山之钟鸣于地。山崩于西而汉宫之钟应于东。或者此钟一鸣。能使娑婆声闻之界一切圆通。忠臣烈士。闻之而奋厉勇迅。奸臣恶子。闻之而遁散沮缩。如积阴溃而乾坤豁。如大寐觉而日月明。庶见冠冕器服不改乎旧。礼乐征伐咸归于 上。此则余区区涕泣投诚之愿。虽未尝与二僧道。心香上升。诸佛其闻之矣。今年冬。家居閒暇。抚念去年此时。惊流光之迅驶。感物化之纷纶。演若怖头。岂云痛定毗耶。杜口聊以示疾。二僧来言钟已成矣。其重若干斤。费钱若干。笋业高悬。金绠上絙。訇然鼓之。万窍皆盈。吾将镂版揭辞于其旁。庸以昭檀施诸贤之名。而流传为山中
曰。名蓝胜刹。俱有大钟。吾寺独无之。无以镇重山门。宣畅法教。吾等方募财于善人长者。吾又竭瓶囊之储。将为鲸鱼蒲牢。大奋无畏之音。俾天人䜣合。缁白警省。剑轮闻声而辍苦。汤镬候响而停炽。愿力虽严。魔事多戏。我土晏然。长安甚扰。是为忧耳。余闻之。黯然而伤。忾然而叹。嗟乎追蠡有垂绝之势。觳觫无补衅之图。辅氏之铭。亢草何人。雒阳之簴。清尘何日。彼独何人。能办斯心。积铢两而铸千钧。合调刁而噫大籁。庸以报恩尘刹。护法金汤。李青莲所云雷鼓霆击震大千。摧摺魑魅招灵仙。将于是乎在。此吾士大夫所愧。又不但心羡而已。抑余闻世出世间。原无二法。机缘相凑。声气攸感。隐峰飞杖而贼破。睦州悬鞋而城完。其有功于此方国土。亦已章章矣。霜降于天。而丰山之钟鸣于地。山崩于西而汉宫之钟应于东。或者此钟一鸣。能使娑婆声闻之界一切圆通。忠臣烈士。闻之而奋厉勇迅。奸臣恶子。闻之而遁散沮缩。如积阴溃而乾坤豁。如大寐觉而日月明。庶见冠冕器服不改乎旧。礼乐征伐咸归于 上。此则余区区涕泣投诚之愿。虽未尝与二僧道。心香上升。诸佛其闻之矣。今年冬。家居閒暇。抚念去年此时。惊流光之迅驶。感物化之纷纶。演若怖头。岂云痛定毗耶。杜口聊以示疾。二僧来言钟已成矣。其重若干斤。费钱若干。笋业高悬。金绠上絙。訇然鼓之。万窍皆盈。吾将镂版揭辞于其旁。庸以昭檀施诸贤之名。而流传为山中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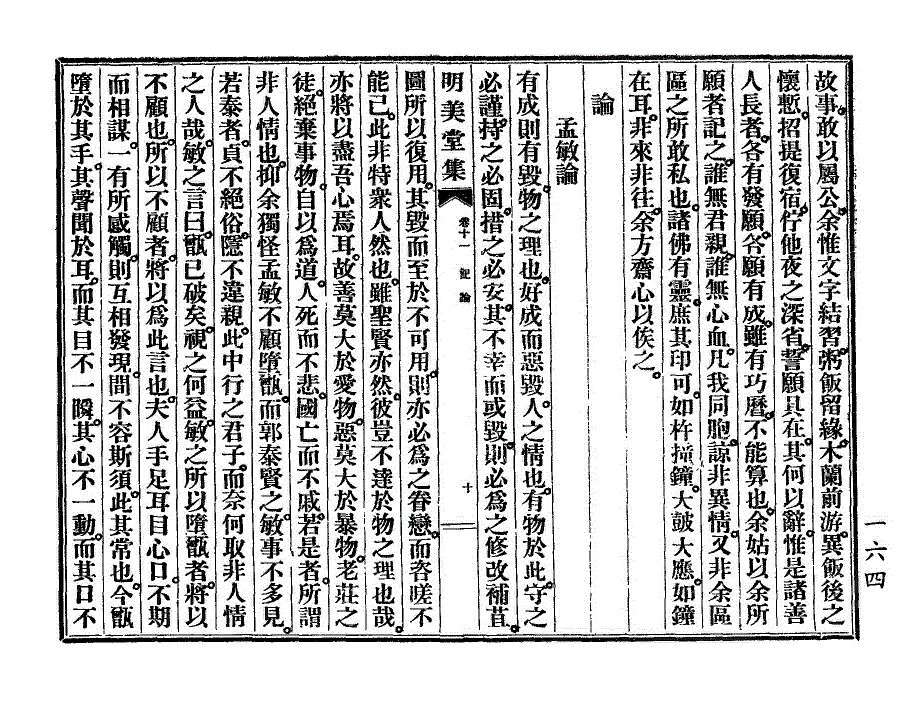 故事。敢以属公。余惟文字结习。粥饭留缘。木兰前游。异饭后之怀惭。招提复宿。伫他夜之深省。誓愿具在。其何以辞。惟是诸善人长者。各有发愿。各愿有成。虽有巧历。不能算也。余姑以余所愿者记之。谁无君亲。谁无心血。凡我同胞。谅非异情。又非余区区之所敢私也。诸佛有灵。庶其印可。如杵撞钟。大鼓大应。如钟在耳。非来非往。余方斋心以俟之。
故事。敢以属公。余惟文字结习。粥饭留缘。木兰前游。异饭后之怀惭。招提复宿。伫他夜之深省。誓愿具在。其何以辞。惟是诸善人长者。各有发愿。各愿有成。虽有巧历。不能算也。余姑以余所愿者记之。谁无君亲。谁无心血。凡我同胞。谅非异情。又非余区区之所敢私也。诸佛有灵。庶其印可。如杵撞钟。大鼓大应。如钟在耳。非来非往。余方斋心以俟之。明美堂集卷十一(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论
孟敏论
有成则有毁。物之理也。好成而恶毁。人之情也。有物于此。守之必谨。持之必固。措之必安。其不幸而或毁。则必为之修改补苴。图所以复用。其毁而至于不可用。则亦必为之眷恋。而咨嗟不能已。此非特众人然也。虽圣贤亦然。彼岂不达于物之理也哉。亦将以尽吾心焉耳。故善莫大于爱物。恶莫大于暴物。老庄之徒。绝弃事物。自以为道。人死而不悲。国亡而不戚。若是者。所谓非人情也。抑余独怪孟敏不顾堕甑。而郭泰贤之。敏事不多见。若泰者。贞不绝俗。隐不违亲。此中行之君子。而奈何取非人情之人哉。敏之言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敏之所以堕甑者。将以不顾也。所以不顾者。将以为此言也。夫人手足耳目心口。不期而相谋。一有所感触。则互相发现。间不容斯须。此其常也。今甑堕于其手。其声闻于耳。而其目不一瞬。其心不一动。而其口不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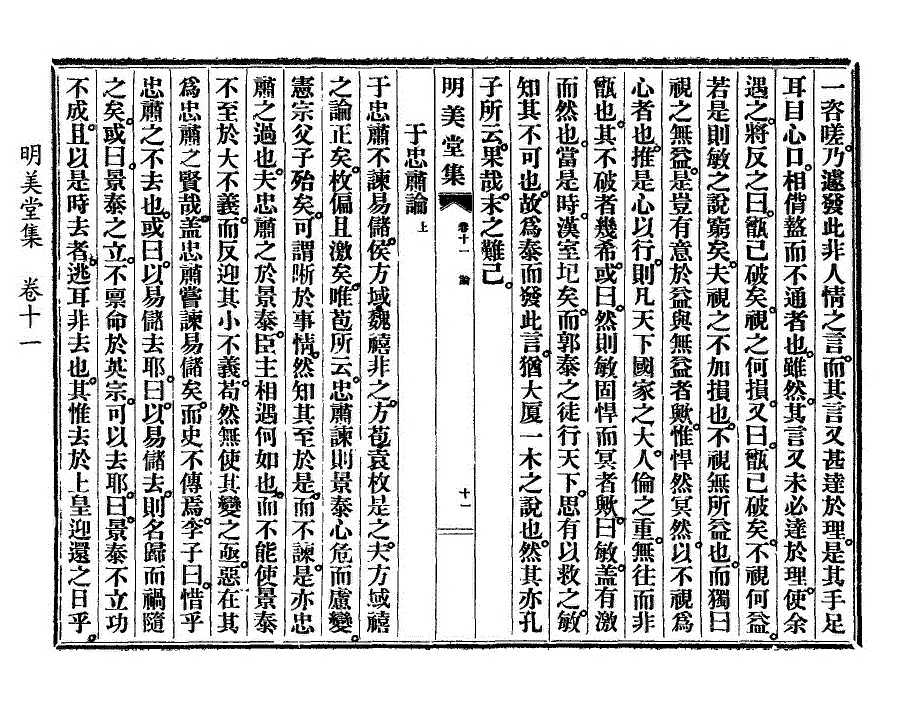 一咨嗟。乃遽发此非人情之言。而其言又甚达于理。是其手足耳目心口。相背盩而不通者也。虽然。其言又未必达于理。使余遇之。将反之曰。甑已破矣。视之何损。又曰。甑已破矣。不视何益。若是则敏之说穷矣。夫视之不加损也。不视无所益也。而独曰视之无益。是岂有意于益与无益者欤。惟悍然冥然。以不视为心者也。推是心以行。则凡天下国家之大。人伦之重。无往而非甑也。其不破者几希。或曰。然则敏固悍而冥者欤。曰敏。盖有激而然也。当是时。汉室圮矣。而郭泰之徒行天下。思有以救之。敏知其不可也。故为泰而发此言。犹大厦一木之说也。然其亦孔子所云。果哉。末之难已。
一咨嗟。乃遽发此非人情之言。而其言又甚达于理。是其手足耳目心口。相背盩而不通者也。虽然。其言又未必达于理。使余遇之。将反之曰。甑已破矣。视之何损。又曰。甑已破矣。不视何益。若是则敏之说穷矣。夫视之不加损也。不视无所益也。而独曰视之无益。是岂有意于益与无益者欤。惟悍然冥然。以不视为心者也。推是心以行。则凡天下国家之大。人伦之重。无往而非甑也。其不破者几希。或曰。然则敏固悍而冥者欤。曰敏。盖有激而然也。当是时。汉室圮矣。而郭泰之徒行天下。思有以救之。敏知其不可也。故为泰而发此言。犹大厦一木之说也。然其亦孔子所云。果哉。末之难已。于忠肃论[上]
于忠肃不谏易储。侯方域,魏禧非之。方苞,袁枚是之。夫方域禧之论正矣。枚偏且激矣。唯苞所云。忠肃谏则景泰心危而虑变。宪宗父子殆矣。可谓晰于事情。然知其至于是。而不谏。是亦忠肃之过也。夫忠肃之于景泰。臣主相遇何如也。而不能使景泰不至于大不义。而反迎其小不义。苟然无使其变之亟。恶在其为忠肃之贤哉。盖忠肃尝谏易储矣。而史不传焉。李子曰。惜乎忠肃之不去也。或曰。以易储去耶。曰。以易储去。则名归而祸随之矣。或曰。景泰之立。不禀命于英宗。可以去耶。曰。景泰不立功不成。且以是时去者。逃耳非去也。其惟去于上皇迎还之日乎。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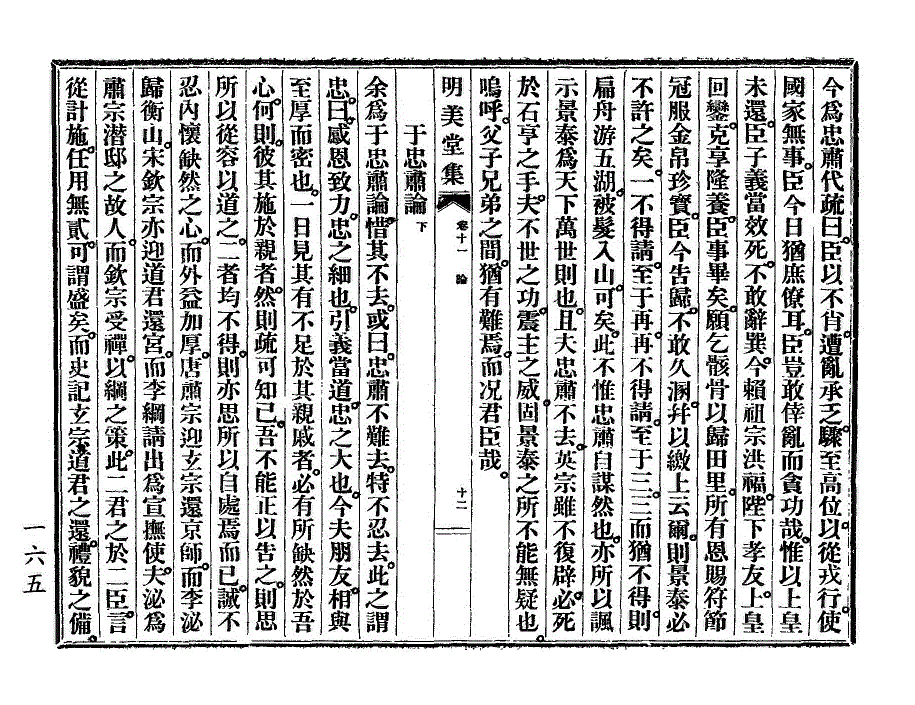 今为忠肃代疏曰。臣以不肖。遭乱承乏。骤至高位。以从戎行。使国家无事。臣今日犹庶僚耳。臣岂敢倖乱而贪功哉。惟以上皇未还。臣子义当效死。不敢辞巽。今赖祖宗洪福。陛下孝友。上皇回銮。克享隆养。臣事毕矣。愿乞骸骨以归田里。所有恩赐符节冠服金帛珍宝。臣今告归。不敢久溷。并以缴上云尔。则景泰必不许之矣。一不得请。至于再。再不得请。至于三。三而犹不得。则扁舟游五湖。被发入山。可矣。此不惟忠肃自谋然也。亦所以讽示景泰为天下万世则也。且夫忠肃不去。英宗虽不复辟。必死于石亨之手。夫不世之功。震主之威。固景泰之所不能无疑也。呜呼。父子兄弟之间。犹有难焉。而况君臣哉。
今为忠肃代疏曰。臣以不肖。遭乱承乏。骤至高位。以从戎行。使国家无事。臣今日犹庶僚耳。臣岂敢倖乱而贪功哉。惟以上皇未还。臣子义当效死。不敢辞巽。今赖祖宗洪福。陛下孝友。上皇回銮。克享隆养。臣事毕矣。愿乞骸骨以归田里。所有恩赐符节冠服金帛珍宝。臣今告归。不敢久溷。并以缴上云尔。则景泰必不许之矣。一不得请。至于再。再不得请。至于三。三而犹不得。则扁舟游五湖。被发入山。可矣。此不惟忠肃自谋然也。亦所以讽示景泰为天下万世则也。且夫忠肃不去。英宗虽不复辟。必死于石亨之手。夫不世之功。震主之威。固景泰之所不能无疑也。呜呼。父子兄弟之间。犹有难焉。而况君臣哉。于忠肃论[下]
余为于忠肃论。惜其不去。或曰。忠肃不难去。特不忍去。此之谓忠。曰。感恩致力。忠之细也。引义当道。忠之大也。今夫朋友。相与至厚而密也。一日见其有不足于其亲戚者。必有所缺然于吾心。何则。彼其施于亲者。然则疏可知已。吾不能正以告之。则思所以从容以道之。二者均不得。则亦思所以自处焉而已。诚不忍内怀缺然之心。而外益加厚。唐肃宗迎玄宗还京师。而李泌归衡山。宋钦宗亦迎道君还宫。而李纲请出为宣抚使。夫泌为肃宗潜邸之故人。而钦宗受禅。以纲之策。此二君之于二臣。言从计施。任用无贰。可谓盛矣。而史记玄宗,道君之还。礼貌之备。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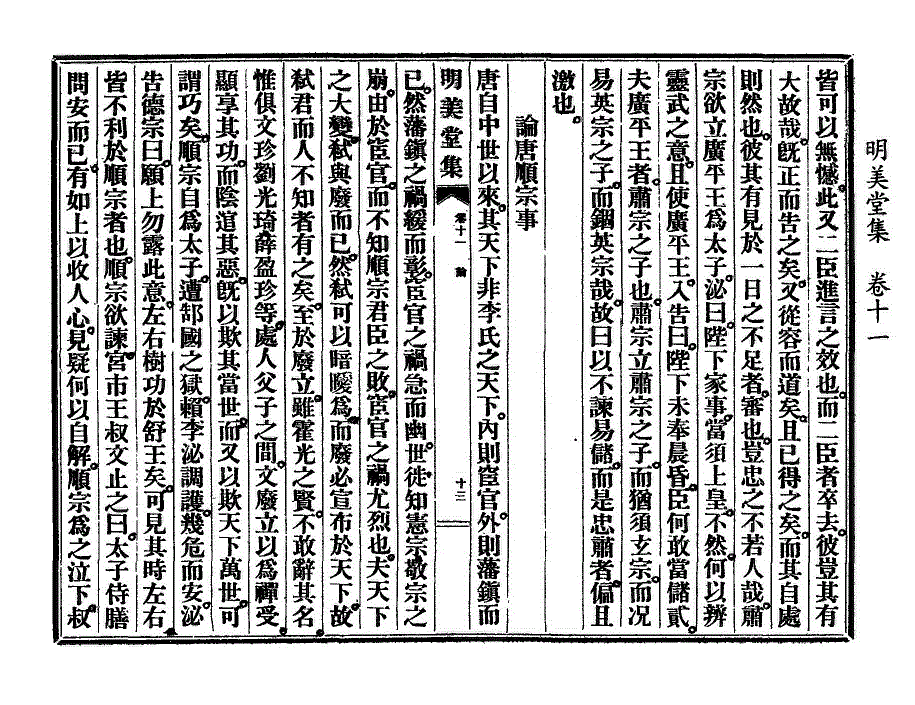 皆可以无憾。此又二臣进言之效也。而二臣者卒去。彼岂其有大故哉。既正而告之矣。又从容而道矣。且已得之矣。而其自处则然也。彼其有见于一日之不足者。审也。岂忠之不若人哉。肃宗欲立广平王为太子。泌曰。陛下家事。当须上皇。不然。何以辨灵武之意。且使广平王。入告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当储贰。夫广平王者。肃宗之子也。肃宗立肃宗之子。而犹须玄宗。而况易英宗之子。而锢英宗哉。故曰以不谏易储。而是忠肃者。偏且激也。
皆可以无憾。此又二臣进言之效也。而二臣者卒去。彼岂其有大故哉。既正而告之矣。又从容而道矣。且已得之矣。而其自处则然也。彼其有见于一日之不足者。审也。岂忠之不若人哉。肃宗欲立广平王为太子。泌曰。陛下家事。当须上皇。不然。何以辨灵武之意。且使广平王。入告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当储贰。夫广平王者。肃宗之子也。肃宗立肃宗之子。而犹须玄宗。而况易英宗之子。而锢英宗哉。故曰以不谏易储。而是忠肃者。偏且激也。论唐顺宗事
唐自中世以来。其天下非李氏之天下。内则宦官。外则藩镇而已。然藩镇之祸缓而彰。宦官之祸急而幽。世徙(一作徒)知宪宗,敬宗之崩。由于宦官。而不知顺宗君臣之败。宦官之祸尤烈也。夫天下之大变。弑与废而已。然弑可以暗暧为。而废必宣布于天下。故弑君而人不知者有之矣。至于废立。虽霍光之贤。不敢辞其名。惟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处人父子之间。文废立以为禅受。显享其功。而阴逭其恶。既以欺其当世。而又以欺天下万世。可谓巧矣。顺宗自为太子。遭郜国之狱。赖李泌调护。几危而安。泌告德宗曰。愿上勿露此意。左右树功于舒王矣。可见其时左右。皆不利于顺宗者也。顺宗欲谏。宫市王叔文止之曰。太子侍膳问安而已。有如上以收人心。见疑何以自解。顺宗为之泣下。叔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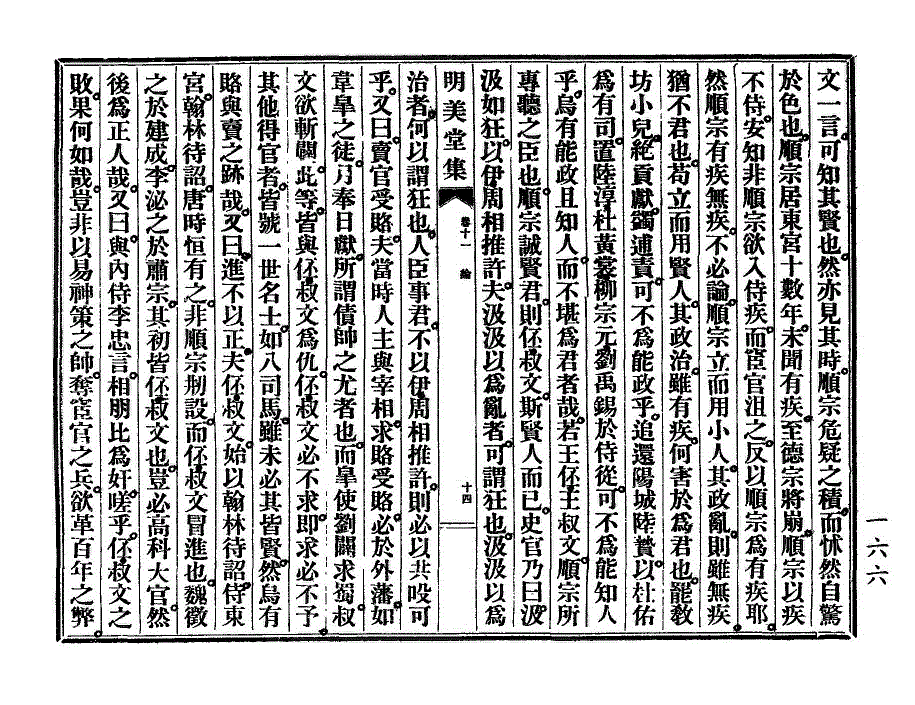 文一言。可知其贤也。然亦见其时。顺宗危疑之积。而怵然自惊于色也。顺宗居东宫十数年。未闻有疾。至德宗将崩。顺宗以疾不侍。安知非顺宗欲入侍疾。而宦官沮之。反以顺宗为有疾耶。然顺宗有疾无疾。不必论。顺宗立而用小人。其政乱。则虽无疾。犹不君也。苟立而用贤人。其政治。虽有疾。何害于为君也。罢教坊小儿。绝贡献。蠲逋责。可不为能政乎。追还阳城陆贽。以杜佑为有司。置陆淳,杜黄裳,柳宗元,刘禹锡于侍从。可不为能知人乎。乌有能政且知人。而不堪为君者哉。若王伾,王叔文。顺宗所专听之臣也。顺宗诚贤君。则伾,叔文。斯贤人而已。史官乃曰。汲汲如狂。以伊,周相推许。夫汲汲以为乱者。可谓狂也。汲汲以为治者。何以谓狂也。人臣事君。不以伊,周相推许。则必以共吺可乎。又曰。卖官受赂。夫当时人主与宰相。求赂受赂。必于外藩。如韦皋之徒。月奉日献。所谓债帅之尤者也。而皋使刘辟求蜀。叔文欲斩辟。此等。皆与伾,叔文为仇。伾,叔文必不求。即求必不予。其他得官者。皆号一世名士。如八司马。虽未必其皆贤。然乌有赂与卖之迹哉。又曰。进不以正。夫伾,叔文。始以翰林待诏。侍东宫。翰林待诏。唐时恒有之。非顺宗刱设。而伾,叔文冒进也。魏徵之于建成。李泌之于肃宗。其初皆伾,叔文也。岂必高科大官。然后为正人哉。又曰。与内侍李忠言。相朋比为奸。嗟乎。伾,叔文之败。果何如哉。岂非以易神策之帅。夺宦官之兵。欲革百年之弊。
文一言。可知其贤也。然亦见其时。顺宗危疑之积。而怵然自惊于色也。顺宗居东宫十数年。未闻有疾。至德宗将崩。顺宗以疾不侍。安知非顺宗欲入侍疾。而宦官沮之。反以顺宗为有疾耶。然顺宗有疾无疾。不必论。顺宗立而用小人。其政乱。则虽无疾。犹不君也。苟立而用贤人。其政治。虽有疾。何害于为君也。罢教坊小儿。绝贡献。蠲逋责。可不为能政乎。追还阳城陆贽。以杜佑为有司。置陆淳,杜黄裳,柳宗元,刘禹锡于侍从。可不为能知人乎。乌有能政且知人。而不堪为君者哉。若王伾,王叔文。顺宗所专听之臣也。顺宗诚贤君。则伾,叔文。斯贤人而已。史官乃曰。汲汲如狂。以伊,周相推许。夫汲汲以为乱者。可谓狂也。汲汲以为治者。何以谓狂也。人臣事君。不以伊,周相推许。则必以共吺可乎。又曰。卖官受赂。夫当时人主与宰相。求赂受赂。必于外藩。如韦皋之徒。月奉日献。所谓债帅之尤者也。而皋使刘辟求蜀。叔文欲斩辟。此等。皆与伾,叔文为仇。伾,叔文必不求。即求必不予。其他得官者。皆号一世名士。如八司马。虽未必其皆贤。然乌有赂与卖之迹哉。又曰。进不以正。夫伾,叔文。始以翰林待诏。侍东宫。翰林待诏。唐时恒有之。非顺宗刱设。而伾,叔文冒进也。魏徵之于建成。李泌之于肃宗。其初皆伾,叔文也。岂必高科大官。然后为正人哉。又曰。与内侍李忠言。相朋比为奸。嗟乎。伾,叔文之败。果何如哉。岂非以易神策之帅。夺宦官之兵。欲革百年之弊。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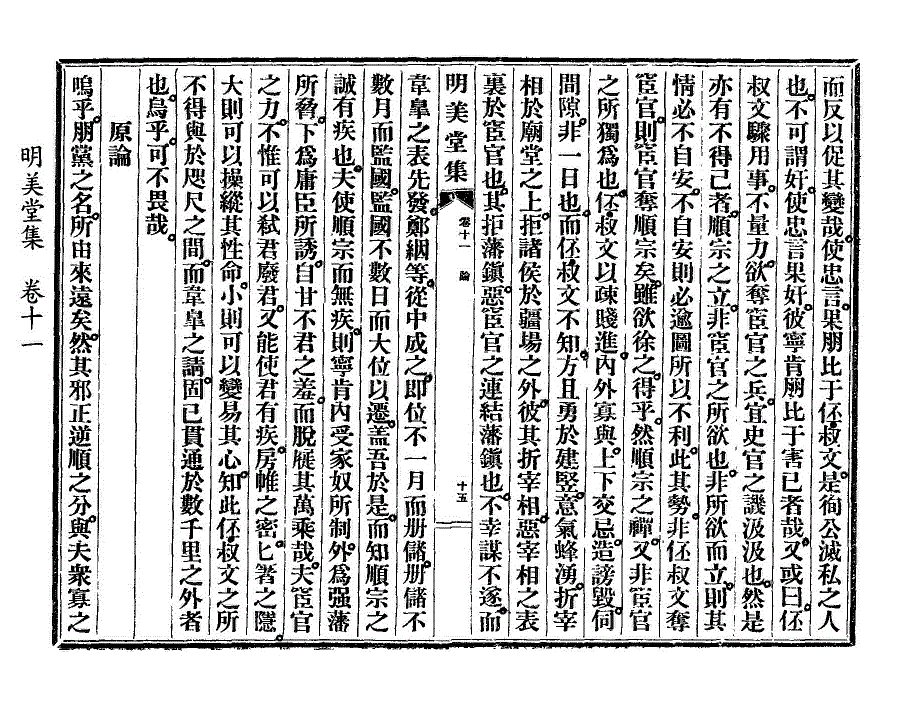 而反以促其变哉。使忠言。果朋比于伾,叔文。是徇公灭私之人也。不可谓奸。使忠言果奸。彼宁肯朋比于害己者哉。又或曰。伾叔文骤用事。不量力。欲夺宦官之兵。宜史官之讥汲汲也。然是亦有不得已者。顺宗之立。非宦官之所欲也。非所欲而立。则其情必不自安。不自安则必逾图所以不利。此其势。非伾叔文夺宦官。则宦官夺顺宗矣。虽欲徐之。得乎。然顺宗之禅。又非宦官之所独为也。伾,叔文以疏贱进。内外寡与。上下交忌。造谤毁。伺间隙。非一日也。而伾,叔文不知。方且勇于建竖。意气蜂涌。折宰相于庙堂之上。拒诸侯于疆场之外。彼其折宰相。恶宰相之表里于宦官也。其拒藩镇。恶宦官之连结藩镇也。不幸谋不遂。而韦皋之表先发。郑絪等。从中成之。即位不一月而册储。册储不数月而监国。监国不数日而大位以迁。盖吾于是。而知顺宗之诚有疾也。夫使顺宗而无疾。则宁肯内受家奴所制。外为强藩所胁。下为庸臣所诱。自甘不君之羞。而脱屣其万乘哉。夫宦官之力。不惟可以弑君废君。又能使君有疾。房帷之密。匕箸之隐。大则可以操纵其性命。小则可以变易其心。知此伾,叔文之所不得与于咫尺之间。而韦皋之请。固已贯通于数千里之外者也。乌乎。可不畏哉。
而反以促其变哉。使忠言。果朋比于伾,叔文。是徇公灭私之人也。不可谓奸。使忠言果奸。彼宁肯朋比于害己者哉。又或曰。伾叔文骤用事。不量力。欲夺宦官之兵。宜史官之讥汲汲也。然是亦有不得已者。顺宗之立。非宦官之所欲也。非所欲而立。则其情必不自安。不自安则必逾图所以不利。此其势。非伾叔文夺宦官。则宦官夺顺宗矣。虽欲徐之。得乎。然顺宗之禅。又非宦官之所独为也。伾,叔文以疏贱进。内外寡与。上下交忌。造谤毁。伺间隙。非一日也。而伾,叔文不知。方且勇于建竖。意气蜂涌。折宰相于庙堂之上。拒诸侯于疆场之外。彼其折宰相。恶宰相之表里于宦官也。其拒藩镇。恶宦官之连结藩镇也。不幸谋不遂。而韦皋之表先发。郑絪等。从中成之。即位不一月而册储。册储不数月而监国。监国不数日而大位以迁。盖吾于是。而知顺宗之诚有疾也。夫使顺宗而无疾。则宁肯内受家奴所制。外为强藩所胁。下为庸臣所诱。自甘不君之羞。而脱屣其万乘哉。夫宦官之力。不惟可以弑君废君。又能使君有疾。房帷之密。匕箸之隐。大则可以操纵其性命。小则可以变易其心。知此伾,叔文之所不得与于咫尺之间。而韦皋之请。固已贯通于数千里之外者也。乌乎。可不畏哉。原论
呜乎。朋党之名。所由来远矣。然其邪正逆顺之分。与夫众寡之
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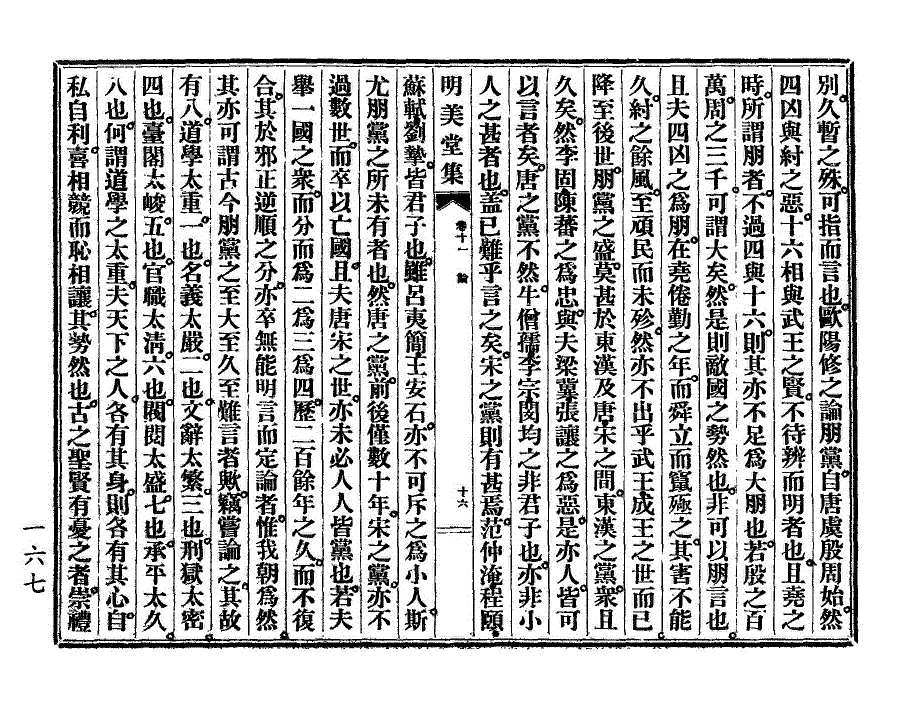 别。久暂之殊。可指而言也。欧阳修之论朋党。自唐虞殷周始。然四凶与纣之恶。十六相与武王之贤。不待辨而明者也。且尧之时。所谓朋者。不过四与十六。则其亦不足为大朋也。若殷之百万。周之三千。可谓大矣。然是则敌国之势然也。非可以朋言也。且夫四凶之为朋。在尧倦勤之年。而舜立而窜殛之。其害不能久。纣之馀风。至顽民而未殄。然亦不出乎武王,成王之世而已。降至后世。朋党之盛。莫甚于东汉及唐,宋之间。东汉之党。众且久矣。然李固,陈蕃之为忠。与夫梁冀,张让之为恶。是亦人。皆可以言者矣。唐之党不然。牛僧孺,李宗,闵均之非君子也。亦非小人之甚者也。盖已难乎言之矣。宋之党则有甚焉。范仲淹,程颐,苏轼,刘挚。皆君子也。虽吕夷简,王安石。亦不可斥之为小人。斯尤朋党之所未有者也。然唐之党。前后仅数十年。宋之党。亦不过数世。而卒以亡国。且夫唐宋之世。亦未必人人皆党也。若夫举一国之众。而分而为二为三为四。历二百馀年之久。而不复合。其于邪正逆顺之分。亦卒无能明言而定论者。惟我朝为然。其亦可谓古今朋党之至大至久至难言者欤。窃尝论之。其故有八。道学太重。一也。名义太严。二也。文辞太繁。三也。刑狱太密。四也。台阁太峻。五也。官职太清。六也。阀阅太盛。七也。承平太久。八也。何谓道学之太重。夫天下之人。各有其身。则各有其心。自私自利。喜相竞而耻相让。其势然也。古之圣贤有忧之者。崇礼
别。久暂之殊。可指而言也。欧阳修之论朋党。自唐虞殷周始。然四凶与纣之恶。十六相与武王之贤。不待辨而明者也。且尧之时。所谓朋者。不过四与十六。则其亦不足为大朋也。若殷之百万。周之三千。可谓大矣。然是则敌国之势然也。非可以朋言也。且夫四凶之为朋。在尧倦勤之年。而舜立而窜殛之。其害不能久。纣之馀风。至顽民而未殄。然亦不出乎武王,成王之世而已。降至后世。朋党之盛。莫甚于东汉及唐,宋之间。东汉之党。众且久矣。然李固,陈蕃之为忠。与夫梁冀,张让之为恶。是亦人。皆可以言者矣。唐之党不然。牛僧孺,李宗,闵均之非君子也。亦非小人之甚者也。盖已难乎言之矣。宋之党则有甚焉。范仲淹,程颐,苏轼,刘挚。皆君子也。虽吕夷简,王安石。亦不可斥之为小人。斯尤朋党之所未有者也。然唐之党。前后仅数十年。宋之党。亦不过数世。而卒以亡国。且夫唐宋之世。亦未必人人皆党也。若夫举一国之众。而分而为二为三为四。历二百馀年之久。而不复合。其于邪正逆顺之分。亦卒无能明言而定论者。惟我朝为然。其亦可谓古今朋党之至大至久至难言者欤。窃尝论之。其故有八。道学太重。一也。名义太严。二也。文辞太繁。三也。刑狱太密。四也。台阁太峻。五也。官职太清。六也。阀阅太盛。七也。承平太久。八也。何谓道学之太重。夫天下之人。各有其身。则各有其心。自私自利。喜相竞而耻相让。其势然也。古之圣贤有忧之者。崇礼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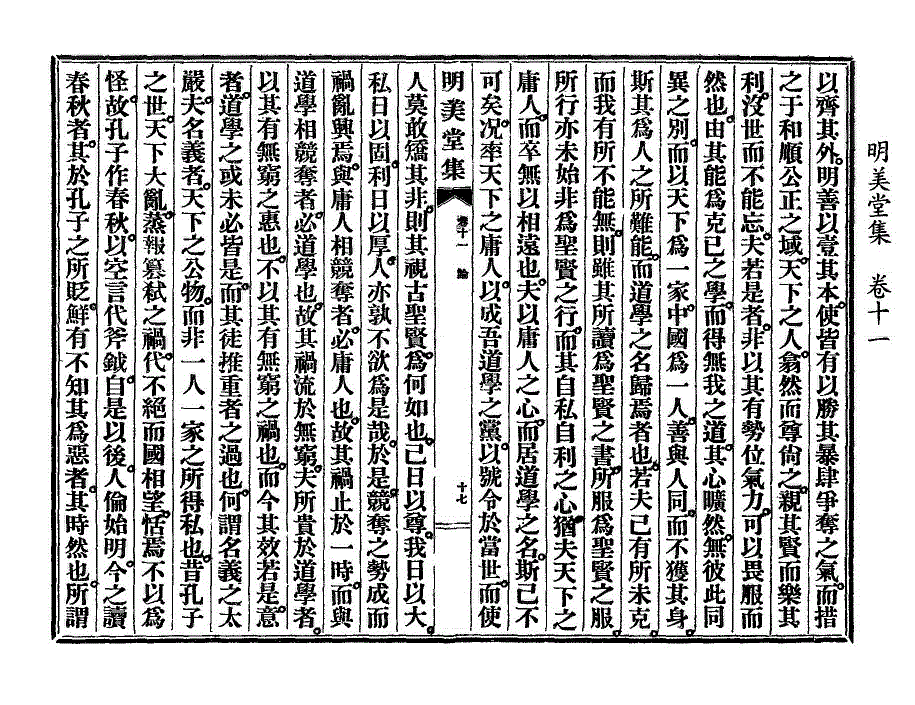 以齐其外。明善以壹其本。使皆有以胜其暴肆争夺之气。而措之于和顺公正之域。天下之人。翕然而尊尚之。亲其贤而乐其利。没世而不能忘。夫若是者。非以其有势位气力。可以畏服而然也。由其能为克己之学。而得无我之道。其心旷然。无彼此同异之别。而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善与人同。而不获其身。斯其为人之所难能。而道学之名归焉者也。若夫己有所未克。而我有所不能无。则虽其所读为圣贤之书。所服为圣贤之服。所行亦未始非为圣贤之行。而其自私自利之心。犹夫天下之庸人。而卒无以相远也。夫以庸人之心。而居道学之名。斯已不可矣。况率天下之庸人。以成吾道学之党。以号令于当世。而使人莫敢矫其非。则其视古圣贤。为何如也。己日以尊。我日以大。私日以固。利日以厚。人亦孰不欲为是哉。于是。竞夺之势成而祸乱兴焉。与庸人相竞夺者。必庸人也。故其祸止于一时。而与道学相竞夺者。必道学也。故其祸流于无穷。夫所贵于道学者。以其有无穷之惠也。不以其有无穷之祸也。而今其效若是。意者。道学之或未必皆是。而其徒推重者之过也。何谓名义之太严。夫名义者。天下之公物。而非一人一家之所得私也。昔孔子之世。天下大乱。蒸报篡弑之祸。代不绝而国相望。恬焉不以为怪。故孔子作春秋。以空言代斧钺。自是以后。人伦始明。今之读春秋者。其于孔子之所贬。鲜有不知其为恶者。其时然也。所谓
以齐其外。明善以壹其本。使皆有以胜其暴肆争夺之气。而措之于和顺公正之域。天下之人。翕然而尊尚之。亲其贤而乐其利。没世而不能忘。夫若是者。非以其有势位气力。可以畏服而然也。由其能为克己之学。而得无我之道。其心旷然。无彼此同异之别。而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善与人同。而不获其身。斯其为人之所难能。而道学之名归焉者也。若夫己有所未克。而我有所不能无。则虽其所读为圣贤之书。所服为圣贤之服。所行亦未始非为圣贤之行。而其自私自利之心。犹夫天下之庸人。而卒无以相远也。夫以庸人之心。而居道学之名。斯已不可矣。况率天下之庸人。以成吾道学之党。以号令于当世。而使人莫敢矫其非。则其视古圣贤。为何如也。己日以尊。我日以大。私日以固。利日以厚。人亦孰不欲为是哉。于是。竞夺之势成而祸乱兴焉。与庸人相竞夺者。必庸人也。故其祸止于一时。而与道学相竞夺者。必道学也。故其祸流于无穷。夫所贵于道学者。以其有无穷之惠也。不以其有无穷之祸也。而今其效若是。意者。道学之或未必皆是。而其徒推重者之过也。何谓名义之太严。夫名义者。天下之公物。而非一人一家之所得私也。昔孔子之世。天下大乱。蒸报篡弑之祸。代不绝而国相望。恬焉不以为怪。故孔子作春秋。以空言代斧钺。自是以后。人伦始明。今之读春秋者。其于孔子之所贬。鲜有不知其为恶者。其时然也。所谓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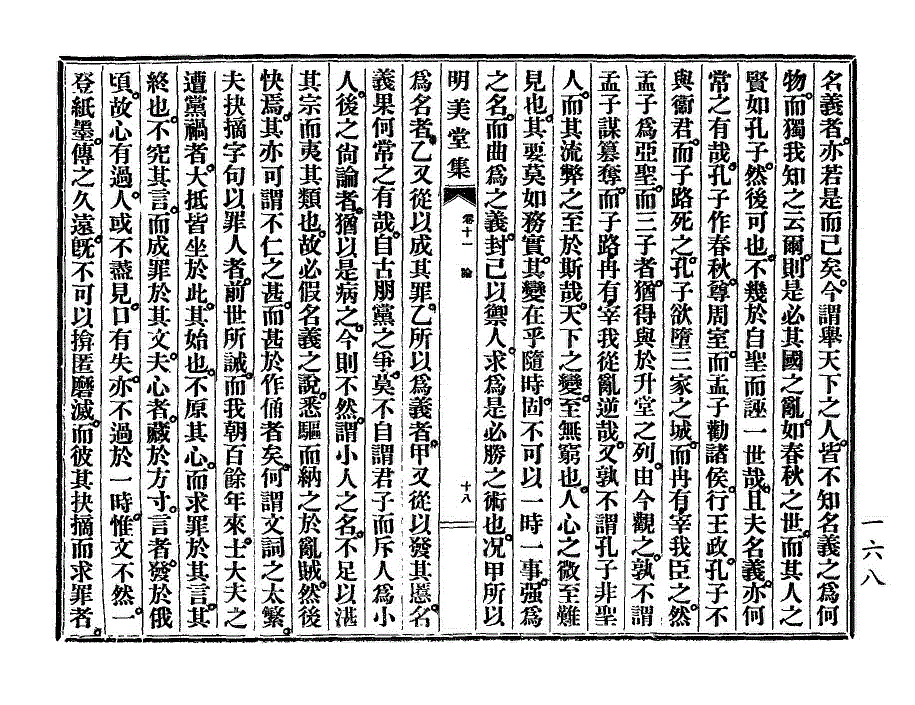 名义者。亦若是而已矣。今谓举天下之人。皆不知名义之为何物。而独我知之云尔。则是必其国之乱。如春秋之世。而其人之贤如孔子。然后可也。不几于自圣而诬一世哉。且夫名义。亦何常之有哉。孔子作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诸侯。行王政。孔子不与卫君。而子路死之。孔子欲堕三家之城。而冉有,宰我臣之。然孟子为亚圣。而三子者。犹得与于升堂之列。由今观之。孰不谓孟子谋篡夺。而子路,冉有,宰我从乱逆哉。又孰不谓孔子非圣人。而其流弊之至于斯哉。天下之变。至无穷也。人心之微至难见也。其要莫如务实。其变在乎随时。固不可以一时一事。强为之名。而曲为之义。封己以御人。求为是必胜之术也。况甲所以为名者。乙又从以成其罪。乙所以为义者。甲又从以发其慝。名义果何常之有哉。自古朋党之争。莫不自谓君子而斥人为小人。后之尚论者。犹以是病之。今则不然。谓小人之名。不足以湛其宗而夷其类也。故必假名义之说。悉驱而纳之于乱贼。然后快焉。其亦可谓不仁之甚。而甚于作俑者矣。何谓文词之太繁。夫抉摘字句以罪人者。前世所诫。而我朝百馀年来。士大夫之遭党祸者。大抵皆坐于此。其始也。不原其心。而求罪于其言。其终也。不究其言。而成罪于其文。夫心者。藏于方寸。言者。发于俄顷。故心有过。人或不尽见。口有失。亦不过于一时。惟文不然。一登纸墨。传之久远。既不可以掩匿磨灭。而彼其抉摘而求罪者。
名义者。亦若是而已矣。今谓举天下之人。皆不知名义之为何物。而独我知之云尔。则是必其国之乱。如春秋之世。而其人之贤如孔子。然后可也。不几于自圣而诬一世哉。且夫名义。亦何常之有哉。孔子作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诸侯。行王政。孔子不与卫君。而子路死之。孔子欲堕三家之城。而冉有,宰我臣之。然孟子为亚圣。而三子者。犹得与于升堂之列。由今观之。孰不谓孟子谋篡夺。而子路,冉有,宰我从乱逆哉。又孰不谓孔子非圣人。而其流弊之至于斯哉。天下之变。至无穷也。人心之微至难见也。其要莫如务实。其变在乎随时。固不可以一时一事。强为之名。而曲为之义。封己以御人。求为是必胜之术也。况甲所以为名者。乙又从以成其罪。乙所以为义者。甲又从以发其慝。名义果何常之有哉。自古朋党之争。莫不自谓君子而斥人为小人。后之尚论者。犹以是病之。今则不然。谓小人之名。不足以湛其宗而夷其类也。故必假名义之说。悉驱而纳之于乱贼。然后快焉。其亦可谓不仁之甚。而甚于作俑者矣。何谓文词之太繁。夫抉摘字句以罪人者。前世所诫。而我朝百馀年来。士大夫之遭党祸者。大抵皆坐于此。其始也。不原其心。而求罪于其言。其终也。不究其言。而成罪于其文。夫心者。藏于方寸。言者。发于俄顷。故心有过。人或不尽见。口有失。亦不过于一时。惟文不然。一登纸墨。传之久远。既不可以掩匿磨灭。而彼其抉摘而求罪者。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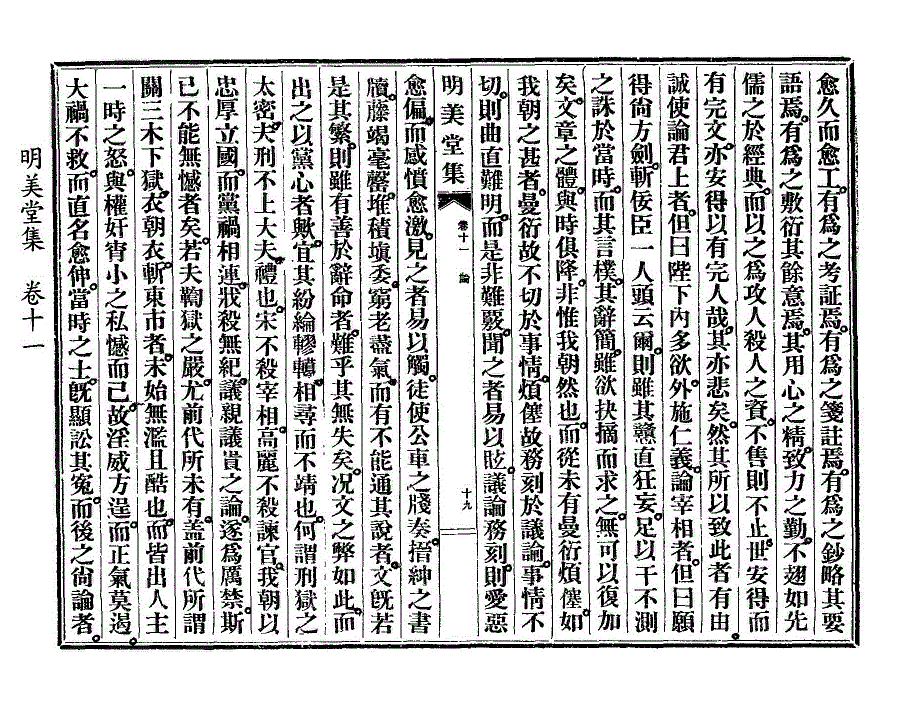 愈久而愈工。有为之考证焉。有为之笺注焉。有为之钞略其要语焉。有为之敷衍其馀意焉。其用心之精。致力之勤。不翅如先儒之于经典。而以之为攻人杀人之资。不售则不止。世安得而有完文。亦安得以有完人哉。其亦悲矣。然其所以致此者有由。诚使论君上者。但曰陛下内多欲。外施仁义。论宰相者。但曰愿得尚方剑。斩佞臣一人头云尔。则虽其戆直狂妄。足以干不测之诛于当时。而其言朴。其辞简。虽欲抉摘而求之。无可以复加矣。文章之体。与时俱降。非惟我朝然也。而从未有曼衍烦僿。如我朝之甚者。曼衍故不切于事情。烦僿故务刻于议论。事情不切。则曲直难明。而是非难覈。闻之者易以眩。议论务刻。则爱恶愈偏。而感愤愈激。见之者易以触。徒使公车之笺奏。搢绅之书牍。藤竭毫罄。堆积填委。穷老尽气。而有不能通其说者。文既若是其繁。则虽有善于辞命者。难乎其无失矣。况文之弊如此。而出之以党心者欤。宜其纷纶轇轕。相寻而不靖也。何谓刑狱之太密。夫刑不上大夫。礼也。宋不杀宰相。高丽不杀谏官。我朝以忠厚立国。而党祸相连。戕杀无纪。议亲议贵之论。遂为厉禁。斯已不能无憾者矣。若夫鞫狱之严。尤前代所未有。盖前代所谓关三木下狱。衣朝衣。斩东市者。未始无滥且酷也。而皆出人主一时之怒。与权奸宵小之私憾而已。故淫威方逞。而正气莫遏。大祸不救。而直名愈伸。当时之士。既显讼其冤。而后之尚论者。
愈久而愈工。有为之考证焉。有为之笺注焉。有为之钞略其要语焉。有为之敷衍其馀意焉。其用心之精。致力之勤。不翅如先儒之于经典。而以之为攻人杀人之资。不售则不止。世安得而有完文。亦安得以有完人哉。其亦悲矣。然其所以致此者有由。诚使论君上者。但曰陛下内多欲。外施仁义。论宰相者。但曰愿得尚方剑。斩佞臣一人头云尔。则虽其戆直狂妄。足以干不测之诛于当时。而其言朴。其辞简。虽欲抉摘而求之。无可以复加矣。文章之体。与时俱降。非惟我朝然也。而从未有曼衍烦僿。如我朝之甚者。曼衍故不切于事情。烦僿故务刻于议论。事情不切。则曲直难明。而是非难覈。闻之者易以眩。议论务刻。则爱恶愈偏。而感愤愈激。见之者易以触。徒使公车之笺奏。搢绅之书牍。藤竭毫罄。堆积填委。穷老尽气。而有不能通其说者。文既若是其繁。则虽有善于辞命者。难乎其无失矣。况文之弊如此。而出之以党心者欤。宜其纷纶轇轕。相寻而不靖也。何谓刑狱之太密。夫刑不上大夫。礼也。宋不杀宰相。高丽不杀谏官。我朝以忠厚立国。而党祸相连。戕杀无纪。议亲议贵之论。遂为厉禁。斯已不能无憾者矣。若夫鞫狱之严。尤前代所未有。盖前代所谓关三木下狱。衣朝衣。斩东市者。未始无滥且酷也。而皆出人主一时之怒。与权奸宵小之私憾而已。故淫威方逞。而正气莫遏。大祸不救。而直名愈伸。当时之士。既显讼其冤。而后之尚论者。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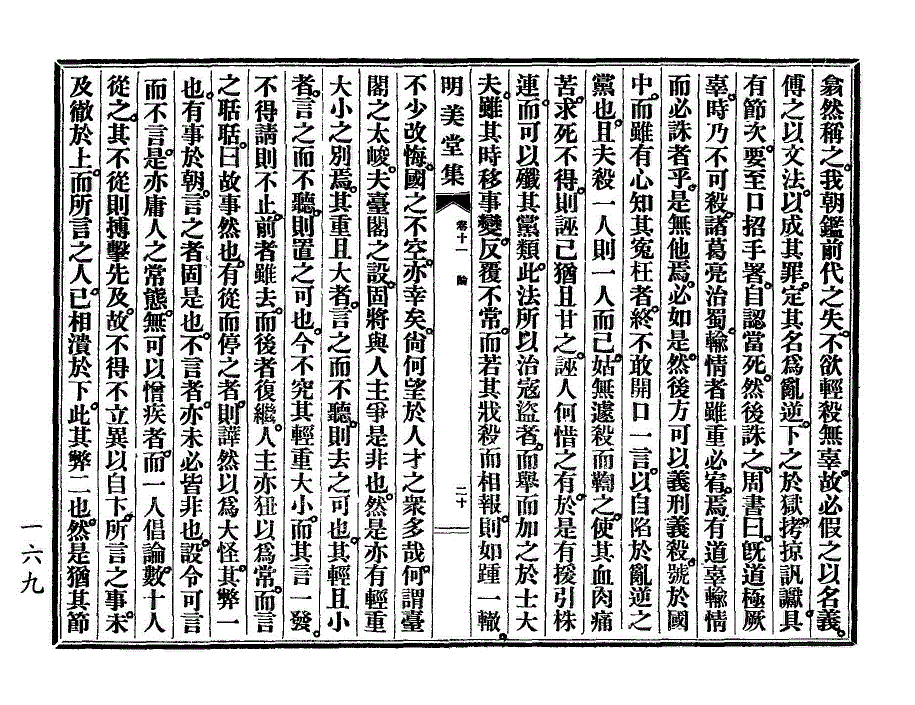 翕然称之。我朝鉴前代之失。不欲轻杀无辜。故必假之以名义。傅之以文法。以成其罪。定其名为乱逆。下之于狱。拷掠訉(一作讯)谳。具有节次。要至口招手署。自认当死。然后诛之。周书曰。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诸葛亮治蜀。输情者虽重必宥。焉有道辜输情而必诛者乎。是无他焉。必如是。然后方可以义刑义杀。号于国中。而虽有心知其冤枉者。终不敢开口一言。以自陷于乱逆之党也。且夫杀一人则一人而已。姑无遽杀而鞫之。使其血肉痛苦。求死不得。则诬己犹且甘之。诬人何惜之有。于是有援引株连。而可以歼其党类。此法所以治寇盗者。而举而加之于士大夫。虽其时移事变。反覆不常。而若其戕杀而相报。则如踵一辙。不少改悔。国之不空。亦幸矣。尚何望于人才之众多哉。何谓台阁之太峻。夫台阁之设。固将与人主争是非也。然是亦有轻重大小之别焉。其重且大者。言之而不听。则去之可也。其轻且小者。言之而不听。则置之可也。今不究其轻重大小。而其言一发。不得请则不止。前者虽去。而后者复继。人主亦狃以为常。而言之聒聒。曰故事然也。有从而停之者。则哗然以为大怪。其弊一也。有事于朝。言之者固是也。不言者。亦未必皆非也。设令可言而不言。是亦庸人之常态。无可以憎疾者。而一人倡论。数十人从之。其不从则搏击先及。故不得不立异以自卞。所言之事。未及彻于上。而所言之人。已相溃于下。此其弊二也。然是犹其节
翕然称之。我朝鉴前代之失。不欲轻杀无辜。故必假之以名义。傅之以文法。以成其罪。定其名为乱逆。下之于狱。拷掠訉(一作讯)谳。具有节次。要至口招手署。自认当死。然后诛之。周书曰。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诸葛亮治蜀。输情者虽重必宥。焉有道辜输情而必诛者乎。是无他焉。必如是。然后方可以义刑义杀。号于国中。而虽有心知其冤枉者。终不敢开口一言。以自陷于乱逆之党也。且夫杀一人则一人而已。姑无遽杀而鞫之。使其血肉痛苦。求死不得。则诬己犹且甘之。诬人何惜之有。于是有援引株连。而可以歼其党类。此法所以治寇盗者。而举而加之于士大夫。虽其时移事变。反覆不常。而若其戕杀而相报。则如踵一辙。不少改悔。国之不空。亦幸矣。尚何望于人才之众多哉。何谓台阁之太峻。夫台阁之设。固将与人主争是非也。然是亦有轻重大小之别焉。其重且大者。言之而不听。则去之可也。其轻且小者。言之而不听。则置之可也。今不究其轻重大小。而其言一发。不得请则不止。前者虽去。而后者复继。人主亦狃以为常。而言之聒聒。曰故事然也。有从而停之者。则哗然以为大怪。其弊一也。有事于朝。言之者固是也。不言者。亦未必皆非也。设令可言而不言。是亦庸人之常态。无可以憎疾者。而一人倡论。数十人从之。其不从则搏击先及。故不得不立异以自卞。所言之事。未及彻于上。而所言之人。已相溃于下。此其弊二也。然是犹其节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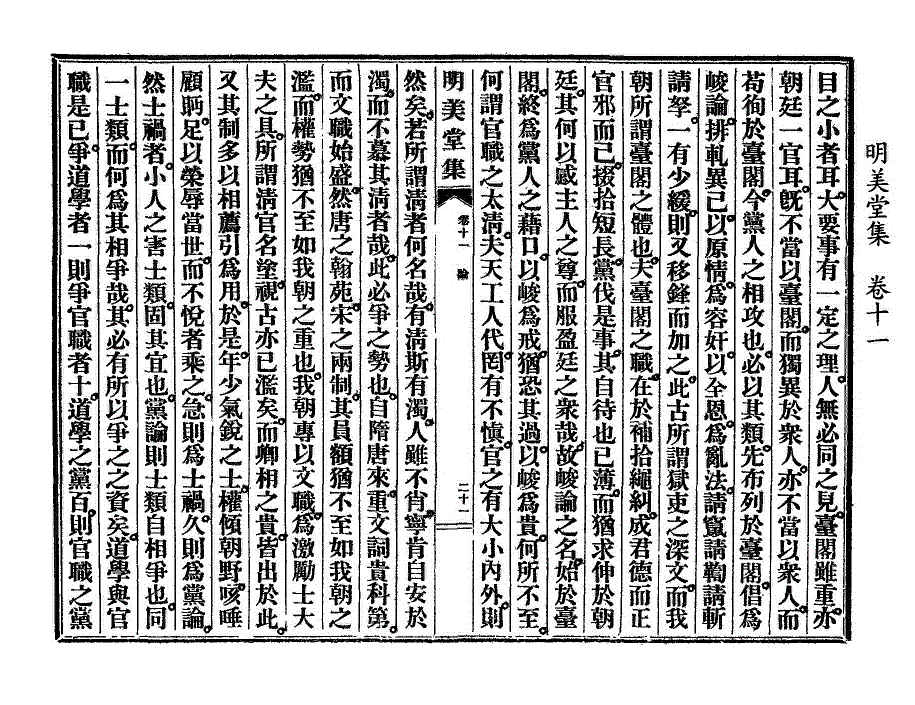 目之小者耳。大要事有一定之理。人无必同之见。台阁虽重。亦朝廷一官耳。既不当以台阁。而独异于众人。亦不当以众人。而苟徇于台阁。今党人之相攻也。必以其类。先布列于台阁。倡为峻论。排轧异己。以原情。为容奸。以全恩。为乱法。请窜请鞫请斩请孥。一有少缓。则又移锋而加之。此古所谓狱吏之深文。而我朝所谓台阁之体也。夫台阁之职。在于补拾绳纠。成君德而正官邪而已。掇拾短长。党伐是事。其自待也已薄。而犹求伸于朝廷。其何以感主人之尊。而服盈廷之众哉。故峻论之名。始于台阁。终为党人之藉口。以峻为戒。犹恐其过。以峻为贵。何所不至。何谓官职之太清。夫天工人代。罔有不慎。官之有大小内外。则然矣。若所谓清者何名哉。有清斯有浊。人虽不肖。宁肯自安于浊。而不慕其清者哉。此必争之势也。自隋唐来。重文词贵科第。而文职始盛。然唐之翰苑。宋之两制。其员额犹不至如我朝之滥。而权势犹不至如我朝之重也。我朝专以文职。为激励士大夫之具。所谓清官名涂。视古亦已滥矣。而卿相之贵。皆出于此。又其制多以相荐引为用。于是。年少气锐之士。权倾朝野。咳唾顾眄。足以荣辱当世。而不悦者乘之。急则为士祸。久则为党论。然士祸者。小人之害士类。固其宜也。党论则士类自相争也。同一士类。而何为其相争哉。其必有所以争之之资矣。道学与官职是已。争道学者一则争官职者十。道学之党百。则官职之党
目之小者耳。大要事有一定之理。人无必同之见。台阁虽重。亦朝廷一官耳。既不当以台阁。而独异于众人。亦不当以众人。而苟徇于台阁。今党人之相攻也。必以其类。先布列于台阁。倡为峻论。排轧异己。以原情。为容奸。以全恩。为乱法。请窜请鞫请斩请孥。一有少缓。则又移锋而加之。此古所谓狱吏之深文。而我朝所谓台阁之体也。夫台阁之职。在于补拾绳纠。成君德而正官邪而已。掇拾短长。党伐是事。其自待也已薄。而犹求伸于朝廷。其何以感主人之尊。而服盈廷之众哉。故峻论之名。始于台阁。终为党人之藉口。以峻为戒。犹恐其过。以峻为贵。何所不至。何谓官职之太清。夫天工人代。罔有不慎。官之有大小内外。则然矣。若所谓清者何名哉。有清斯有浊。人虽不肖。宁肯自安于浊。而不慕其清者哉。此必争之势也。自隋唐来。重文词贵科第。而文职始盛。然唐之翰苑。宋之两制。其员额犹不至如我朝之滥。而权势犹不至如我朝之重也。我朝专以文职。为激励士大夫之具。所谓清官名涂。视古亦已滥矣。而卿相之贵。皆出于此。又其制多以相荐引为用。于是。年少气锐之士。权倾朝野。咳唾顾眄。足以荣辱当世。而不悦者乘之。急则为士祸。久则为党论。然士祸者。小人之害士类。固其宜也。党论则士类自相争也。同一士类。而何为其相争哉。其必有所以争之之资矣。道学与官职是已。争道学者一则争官职者十。道学之党百。则官职之党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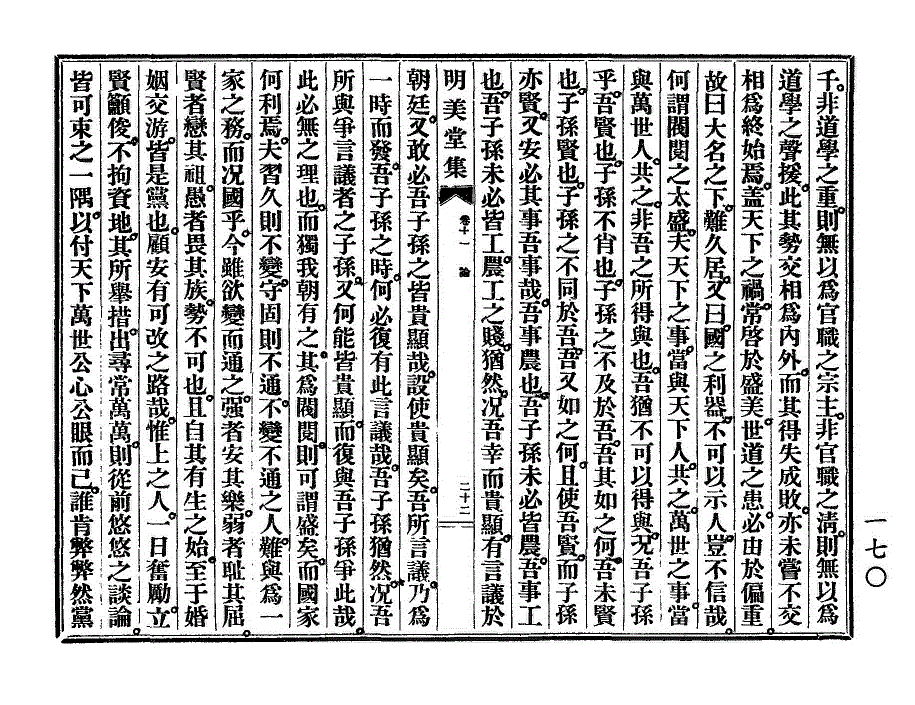 千。非道学之重。则无以为官职之宗主。非官职之清。则无以为道学之声援。此其势交相为内外。而其得失成败。亦未尝不交相为终始焉。盖天下之祸。常启于盛美。世道之患。必由于偏重。故曰大名之下。难久居。又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岂不信哉。何谓阀阅之太盛。夫天下之事。当与天下人。共之。万世之事。当与万世人。共之。非吾之所得与也。吾犹不可以得与。况吾子孙乎。吾贤也。子孙不肖也。子孙之不及于吾。吾其如之何。吾未贤也。子孙贤也。子孙之不同于吾。吾又如之何。且使吾贤。而子孙亦贤。又安必其事吾事哉。吾事农也。吾子孙未必皆农。吾事工也。吾子孙未必皆工。农工之贱。犹然。况吾幸而贵显。有言议于朝廷。又敢必吾子孙之皆贵显哉。设使贵显矣。吾所言议。乃为一时而发。吾子孙之时。何必复有此言议哉。吾子孙犹然。况吾所与争言议者之子孙。又何能皆贵显。而复与吾子孙争此哉。此必无之理也。而独我朝有之。其为阀阅。则可谓盛矣。而国家何利焉。夫习久则不变。守固则不通。不变不通之人。难与为一家之务。而况国乎。今虽欲变而通之。强者安其乐。弱者耻其屈。贤者恋其祖。愚者畏其族。势不可也。且自其有生之始。至于婚姻交游。皆是党也。顾安有可改之路哉。惟上之人。一日奋励。立贤吁俊。不拘资地。其所举措。出寻常万万。则从前悠悠之谈论。皆可束之一隅。以付天下万世公心公眼而已。谁肯弊弊然党
千。非道学之重。则无以为官职之宗主。非官职之清。则无以为道学之声援。此其势交相为内外。而其得失成败。亦未尝不交相为终始焉。盖天下之祸。常启于盛美。世道之患。必由于偏重。故曰大名之下。难久居。又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岂不信哉。何谓阀阅之太盛。夫天下之事。当与天下人。共之。万世之事。当与万世人。共之。非吾之所得与也。吾犹不可以得与。况吾子孙乎。吾贤也。子孙不肖也。子孙之不及于吾。吾其如之何。吾未贤也。子孙贤也。子孙之不同于吾。吾又如之何。且使吾贤。而子孙亦贤。又安必其事吾事哉。吾事农也。吾子孙未必皆农。吾事工也。吾子孙未必皆工。农工之贱。犹然。况吾幸而贵显。有言议于朝廷。又敢必吾子孙之皆贵显哉。设使贵显矣。吾所言议。乃为一时而发。吾子孙之时。何必复有此言议哉。吾子孙犹然。况吾所与争言议者之子孙。又何能皆贵显。而复与吾子孙争此哉。此必无之理也。而独我朝有之。其为阀阅。则可谓盛矣。而国家何利焉。夫习久则不变。守固则不通。不变不通之人。难与为一家之务。而况国乎。今虽欲变而通之。强者安其乐。弱者耻其屈。贤者恋其祖。愚者畏其族。势不可也。且自其有生之始。至于婚姻交游。皆是党也。顾安有可改之路哉。惟上之人。一日奋励。立贤吁俊。不拘资地。其所举措。出寻常万万。则从前悠悠之谈论。皆可束之一隅。以付天下万世公心公眼而已。谁肯弊弊然党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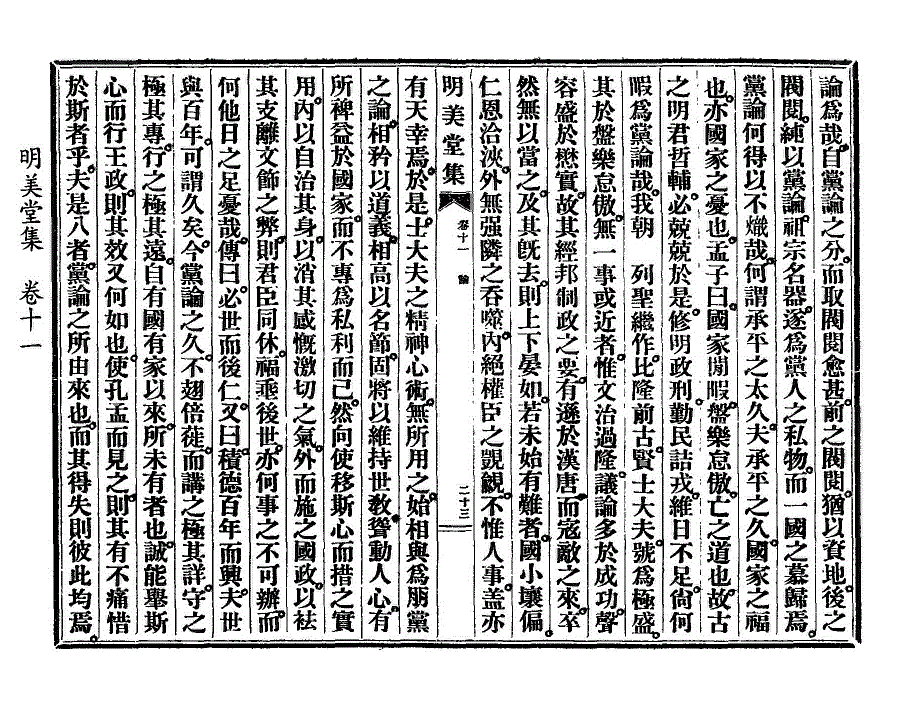 论为哉。自党论之分。而取阀阅愈甚。前之阀阅。犹以资地。后之阀阅。纯以党论祖宗名器。遂为党人之私物。而一国之慕归焉。党论何得以不炽哉。何谓承平之太久。夫承平之久。国家之福也。亦国家之忧也。孟子曰。国家閒暇。盘乐怠傲。亡之道也。故古之明君哲辅。必兢兢于是。修明政刑。勤民诘戎。维日不足。尚何暇为党论哉。我朝 列圣继作。比隆前古。贤士大夫。号为极盛。其于盘乐怠傲。无一事或近者。惟文治过隆。议论多于成功。声容盛于懋实。故其经邦制政之要。有逊于汉唐。而寇敌之来。卒然无以当之。及其既去。则上下晏如。若未始有难者。国小壤偏。仁恩洽浃。外无强邻之吞噬。内绝权臣之觊觎。不惟人事。盖亦有天幸焉。于是。士大夫之精神心术。无所用之。始相与为朋党之论。相矜以道义。相高以名节。固将以维持世教。耸动人心。有所裨益于国家。而不专为私利而已。然向使移斯心而措之实用。内以自治其身。以消其感慨激切之气。外而施之国政。以袪其支离文饰之弊。则君臣同休。福垂后世。亦何事之不可办。而何他日之足忧哉。传曰。必世而后仁。又曰。积德百年而兴。夫世与百年。可谓久矣。今党论之久。不翅倍蓰。而讲之极其详。守之极其专。行之极其远。自有国有家以来。所未有者也。诚能举斯心而行王政。则其效又何如也。使孔孟而见之。则其有不痛惜于斯者乎。夫是八者。党论之所由来也。而其得失则彼此均焉。
论为哉。自党论之分。而取阀阅愈甚。前之阀阅。犹以资地。后之阀阅。纯以党论祖宗名器。遂为党人之私物。而一国之慕归焉。党论何得以不炽哉。何谓承平之太久。夫承平之久。国家之福也。亦国家之忧也。孟子曰。国家閒暇。盘乐怠傲。亡之道也。故古之明君哲辅。必兢兢于是。修明政刑。勤民诘戎。维日不足。尚何暇为党论哉。我朝 列圣继作。比隆前古。贤士大夫。号为极盛。其于盘乐怠傲。无一事或近者。惟文治过隆。议论多于成功。声容盛于懋实。故其经邦制政之要。有逊于汉唐。而寇敌之来。卒然无以当之。及其既去。则上下晏如。若未始有难者。国小壤偏。仁恩洽浃。外无强邻之吞噬。内绝权臣之觊觎。不惟人事。盖亦有天幸焉。于是。士大夫之精神心术。无所用之。始相与为朋党之论。相矜以道义。相高以名节。固将以维持世教。耸动人心。有所裨益于国家。而不专为私利而已。然向使移斯心而措之实用。内以自治其身。以消其感慨激切之气。外而施之国政。以袪其支离文饰之弊。则君臣同休。福垂后世。亦何事之不可办。而何他日之足忧哉。传曰。必世而后仁。又曰。积德百年而兴。夫世与百年。可谓久矣。今党论之久。不翅倍蓰。而讲之极其详。守之极其专。行之极其远。自有国有家以来。所未有者也。诚能举斯心而行王政。则其效又何如也。使孔孟而见之。则其有不痛惜于斯者乎。夫是八者。党论之所由来也。而其得失则彼此均焉。明美堂集卷十一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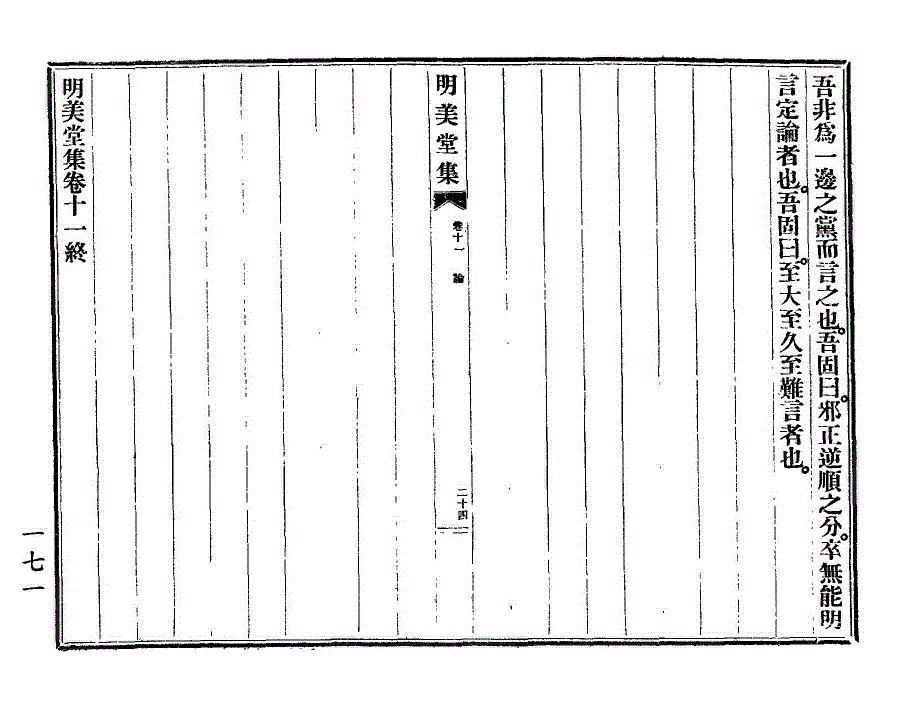 吾非为一边之党而言之也。吾固曰。邪正逆顺之分。卒无能明言定论者也。吾固曰。至大至久至难言者也。
吾非为一边之党而言之也。吾固曰。邪正逆顺之分。卒无能明言定论者也。吾固曰。至大至久至难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