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序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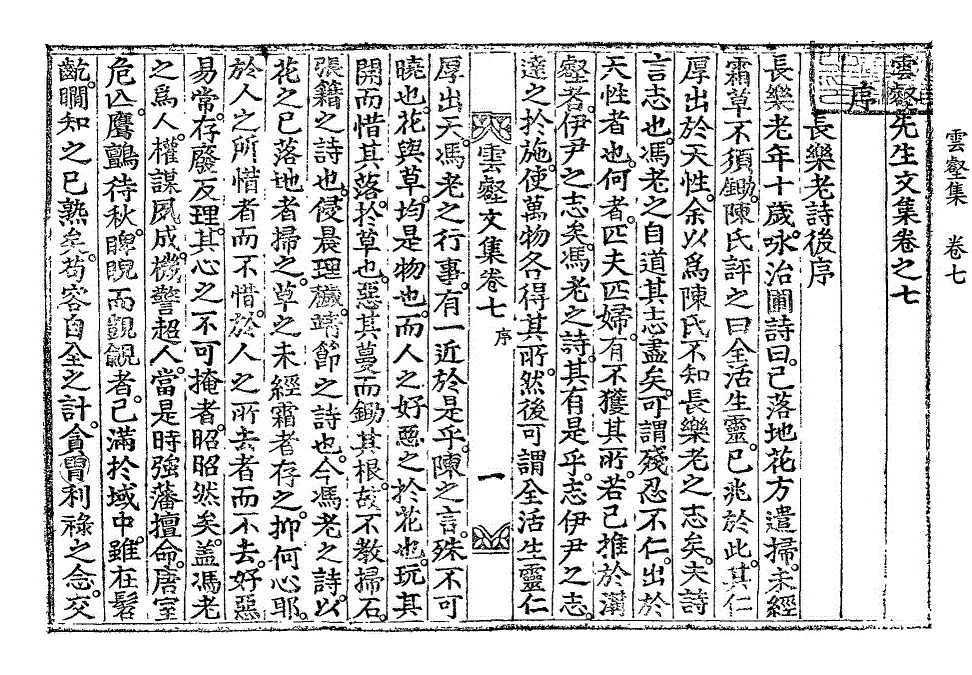 长乐老诗后序
长乐老诗后序长乐老年十岁。咏治圃诗曰。已落地花方遣扫。未经霜草不须锄。陈氏评之曰全活生灵。已兆于此。其仁厚出于天性。余以为陈氏不知长乐老之志矣。夫诗言志也。冯老之自道其志尽矣。可谓残忍不仁。出于天性者也。何者。匹夫匹妇。有不获其所。若已推于沟壑者。伊尹之志矣。冯老之诗。其有是乎。志伊尹之志。达之于施。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可谓全活生灵仁厚出天。冯老之行事。有一近于是乎。陈之言。殊不可晓也。花与草。均是物也。而人之好恶之于花也。玩其开而惜其落。于草也。恶其蔓而锄其根。故不教扫石。张籍之诗也。侵晨理秽。靖节之诗也。今冯老之诗。以花之已落地者扫之。草之未经霜者存之。抑何心耶。于人之所惜者而不惜。于人之所去者而不去。好恶易常。存废反理。其心之不可掩者。昭昭然矣。盖冯老之为人。权谋夙成。机警超人。当是时强藩擅命。唐室危亡。鹰鹯待秋。睥睨而觊觎者。已满于域中。虽在髫龁。瞯知之已熟矣。苟容自全之计。贪胃(一作冒)利禄之念。交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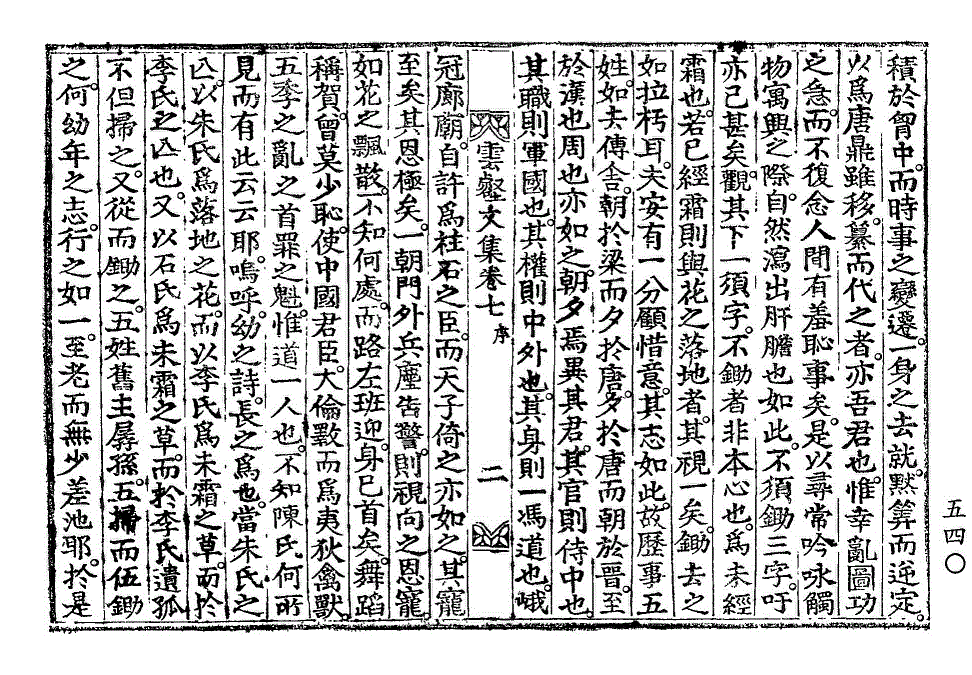 积于胸中。而时事之变迁。一身之去就。默算而逆定。以为唐鼎虽移。纂而代之者。亦吾君也。惟幸乱图功之急。而不复念人间有羞耻事矣。是以寻常吟咏触物寓兴之际。自然泻出肝胆也如此。不须锄三字。吁亦已甚矣。观其下一须字。不锄者非本心也。为未经霜也。若已经霜则与花之落地者。其视一矣。锄去之如拉朽耳。夫安有一分顾惜意。其志如此。故历事五姓。如去传舍。朝于梁而夕于唐。夕于唐而朝于晋。至于汉也周也亦如之。朝夕焉异其君。其官则侍中也。其职则军国也。其权则中外也。其身则一冯道也。峨冠廊庙。自许为柱石之臣。而天子倚之亦如之。其宠至矣其恩极矣。一朝门外兵尘告警。则视向之恩宠。如花之飘散。不知何处。而路左班迎。身已首矣。舞蹈称贺。曾莫少耻。使中国君臣。大伦斁而为夷狄禽兽。五季之乱之首罪之魁。惟道一人也。不知陈氏何所见而有此云云耶。呜呼。幼之诗。长之为也。当朱氏之亡。以朱氏为落地之花。而以李氏为未霜之草。而于李氏之亡也。又以石氏为未霜之草。而于李氏遗孤不但扫之。又从而锄之。五姓旧主孱孙。五扫而伍锄之。何幼年之志。行之如一。至老而无少差池耶。于是
积于胸中。而时事之变迁。一身之去就。默算而逆定。以为唐鼎虽移。纂而代之者。亦吾君也。惟幸乱图功之急。而不复念人间有羞耻事矣。是以寻常吟咏触物寓兴之际。自然泻出肝胆也如此。不须锄三字。吁亦已甚矣。观其下一须字。不锄者非本心也。为未经霜也。若已经霜则与花之落地者。其视一矣。锄去之如拉朽耳。夫安有一分顾惜意。其志如此。故历事五姓。如去传舍。朝于梁而夕于唐。夕于唐而朝于晋。至于汉也周也亦如之。朝夕焉异其君。其官则侍中也。其职则军国也。其权则中外也。其身则一冯道也。峨冠廊庙。自许为柱石之臣。而天子倚之亦如之。其宠至矣其恩极矣。一朝门外兵尘告警。则视向之恩宠。如花之飘散。不知何处。而路左班迎。身已首矣。舞蹈称贺。曾莫少耻。使中国君臣。大伦斁而为夷狄禽兽。五季之乱之首罪之魁。惟道一人也。不知陈氏何所见而有此云云耶。呜呼。幼之诗。长之为也。当朱氏之亡。以朱氏为落地之花。而以李氏为未霜之草。而于李氏之亡也。又以石氏为未霜之草。而于李氏遗孤不但扫之。又从而锄之。五姓旧主孱孙。五扫而伍锄之。何幼年之志。行之如一。至老而无少差池耶。于是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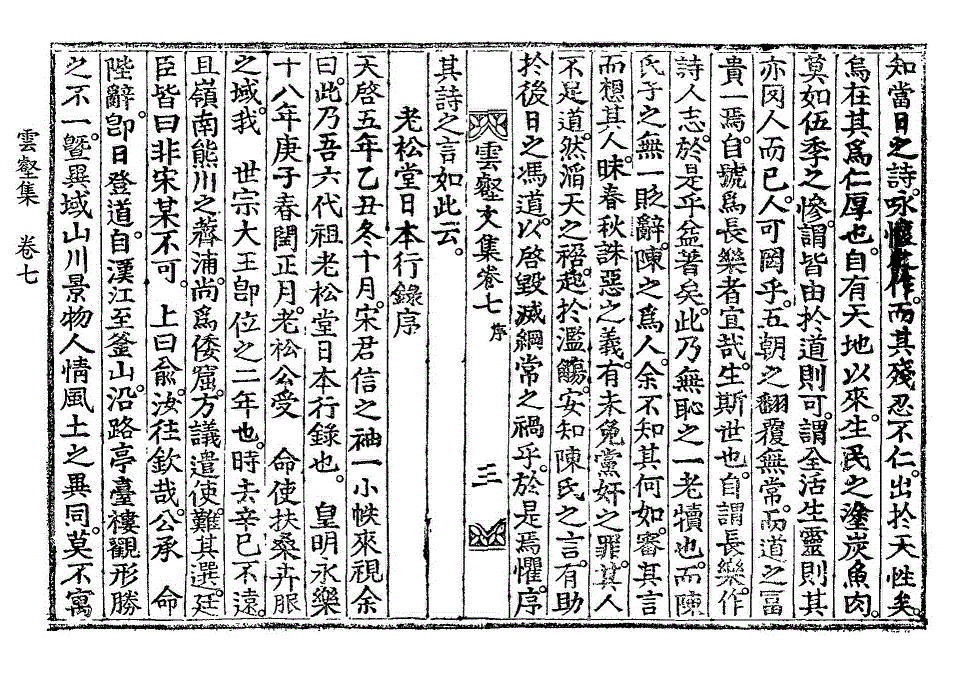 知当日之诗。咏怀之作。而其残忍不仁。出于天性矣。乌在其为仁厚也。自有天地以来。生民之涂炭鱼肉。莫如伍季之惨。谓皆由于道则可。谓全活生灵则其亦罔人而已。人可罔乎。五朝之翻覆无常。而道之富贵一焉。自号为长乐者宜哉。生斯世也。自谓长乐。作诗人志。于是乎益著矣。此乃无耻之一老犊也。而陈氏子之无一贬辞。陈之为人。余不知其何如。审其言而想其人。昧春秋诛恶之义。有未免党奸之罪。其人不足道。然滔天之𥚁。起于滥觞。安知陈氏之言。有助于后日之冯道。以启毁灭纲常之祸乎。于是焉惧。序其诗之言如此云。
知当日之诗。咏怀之作。而其残忍不仁。出于天性矣。乌在其为仁厚也。自有天地以来。生民之涂炭鱼肉。莫如伍季之惨。谓皆由于道则可。谓全活生灵则其亦罔人而已。人可罔乎。五朝之翻覆无常。而道之富贵一焉。自号为长乐者宜哉。生斯世也。自谓长乐。作诗人志。于是乎益著矣。此乃无耻之一老犊也。而陈氏子之无一贬辞。陈之为人。余不知其何如。审其言而想其人。昧春秋诛恶之义。有未免党奸之罪。其人不足道。然滔天之𥚁。起于滥觞。安知陈氏之言。有助于后日之冯道。以启毁灭纲常之祸乎。于是焉惧。序其诗之言如此云。老松堂日本行录序
天启五年乙丑冬十月。宋君信之袖一小帙来视余曰。此乃吾六代祖老松堂日本行录也。 皇明永乐十八年庚子春闰正月。老松公受 命使扶桑卉服之域。我 世宗大王即位之二年也。时去辛巳不远。且岭南熊川之荠浦。尚为倭窟。方议遣使。难其选。廷臣皆曰非宋某不可。 上曰俞。汝往钦哉。公承 命陛辞。即日登道。自汉江至釜山。沿路亭台楼观形胜之不一。暨异域山川景物人情风土之异同。莫不寓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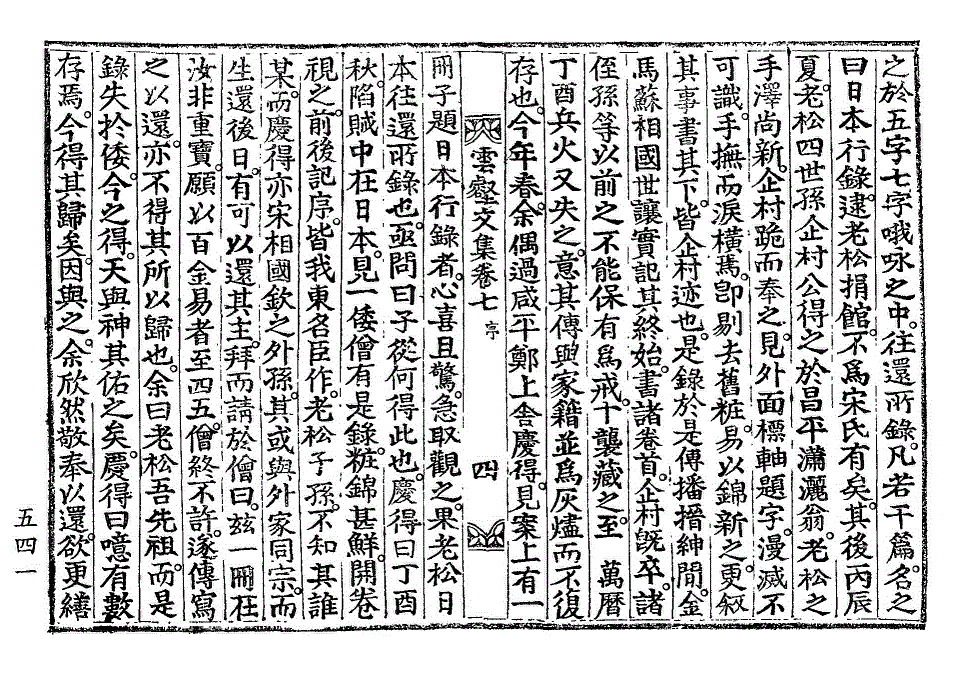 之于五字七字哦咏之中。往还所录。凡若干篇。名之曰日本行录。逮老松捐馆。不为宋氏有矣。其后丙辰夏。老松四世孙企村公得之于昌平潇洒翁。老松之手泽尚新。企村跪而奉之。见外面标轴题字。漫灭不可识。手抚而泪横焉。即剔去旧妆。易以锦新之。更叙其事书其下。皆企村迹也。是录于是传播搢绅间。金马苏相国世让实记其终始。书诸卷首。企村既卒。诸侄孙等以前之不能保有为戒。十袭藏之。至 万历丁酉兵火又失之。意其传与家籍并为灰烬而不复存也。今年春。余偶过咸平郑上舍庆得。见案上有一册子题日本行录者。心喜且惊。急取观之。果老松日本往还所录也。亟问曰子从何得此也。庆得曰丁酉秋。陷贼中在日本。见一倭僧有是录。妆锦甚鲜。开卷视之。前后记序。皆我东名臣作。老松子孙。不知其谁某。而庆得亦宋相国钦之外孙。其或与外家同宗。而生还后日。有可以还其主。拜而请于僧曰。玆一册在汝非重宝。愿以百金易者至四五。僧终不许。遂传写之以还。亦不得其所以归也。余曰老松吾先祖。而是录失于倭。今之得。天与神其佑之矣。庆得曰噫有数存焉。今得其归矣。因与之。余欣然敬奉以还。欲更缮
之于五字七字哦咏之中。往还所录。凡若干篇。名之曰日本行录。逮老松捐馆。不为宋氏有矣。其后丙辰夏。老松四世孙企村公得之于昌平潇洒翁。老松之手泽尚新。企村跪而奉之。见外面标轴题字。漫灭不可识。手抚而泪横焉。即剔去旧妆。易以锦新之。更叙其事书其下。皆企村迹也。是录于是传播搢绅间。金马苏相国世让实记其终始。书诸卷首。企村既卒。诸侄孙等以前之不能保有为戒。十袭藏之。至 万历丁酉兵火又失之。意其传与家籍并为灰烬而不复存也。今年春。余偶过咸平郑上舍庆得。见案上有一册子题日本行录者。心喜且惊。急取观之。果老松日本往还所录也。亟问曰子从何得此也。庆得曰丁酉秋。陷贼中在日本。见一倭僧有是录。妆锦甚鲜。开卷视之。前后记序。皆我东名臣作。老松子孙。不知其谁某。而庆得亦宋相国钦之外孙。其或与外家同宗。而生还后日。有可以还其主。拜而请于僧曰。玆一册在汝非重宝。愿以百金易者至四五。僧终不许。遂传写之以还。亦不得其所以归也。余曰老松吾先祖。而是录失于倭。今之得。天与神其佑之矣。庆得曰噫有数存焉。今得其归矣。因与之。余欣然敬奉以还。欲更缮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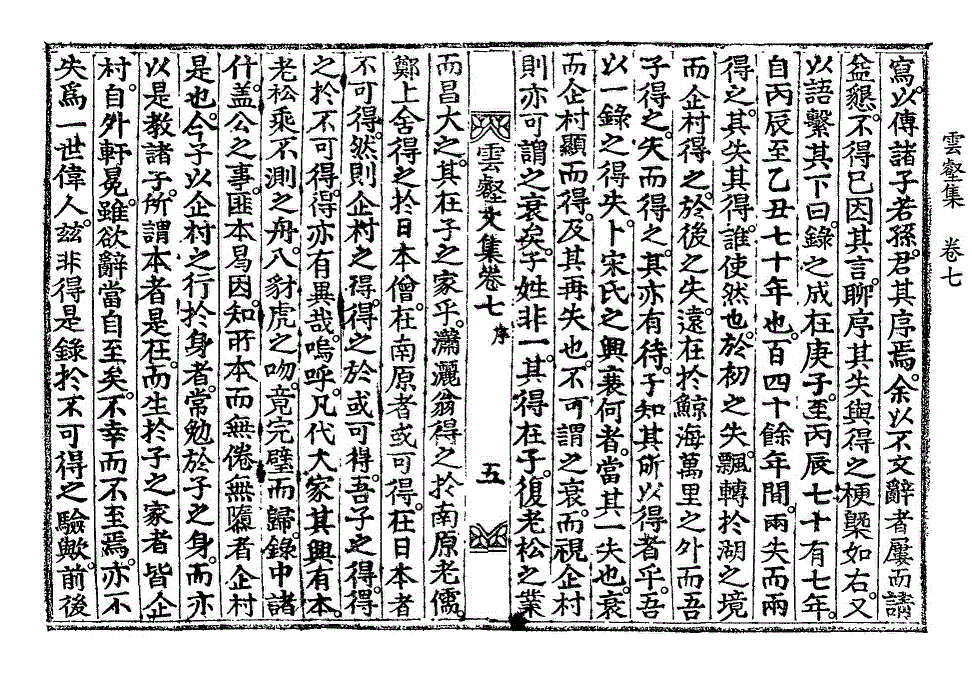 写。以传诸子若孙。君其序焉。余以不文辞者屡而请益恳。不得已因其言。聊序其失与得之梗槩如右。又以语系其下曰。录之成在庚子。至丙辰七十有七年。自丙辰至乙丑七十年也。百四十馀年间。两失而两得之。其失其得。谁使然也。于初之失。飘转于湖之境而企村得之。于后之失。远在于鲸海万里之外而吾子得之。失而得之。其亦有待。子知其所以得者乎。吾以一录之得失。卜宋氏之兴衰何者。当其一失也。衰而企村显而得。及其再失也。不可谓之衰。而视企村则亦可谓之衰矣。子姓非一。其得在子。复老松之业而昌大之。其在子之家乎。潇洒翁得之于南原老儒。郑上舍得之于日本僧。在南原者或可得。在日本者不可得。然则企村之得。得之于或可得。吾子之得。得之于不可得。得亦有异哉。呜呼。凡代大家其兴有本。老松乘不测之舟。入豺虎之吻。竟完璧而归。录中诸什。盖公之事。匪本曷因。知所本而无倦无隳者企村是也。今子以企村之行于身者。常勉于子之身。而亦以是教诸子。所谓本者是在。而生于子之家者皆企村。自外轩冕。虽欲辞当自至矣。不幸而不至焉。亦不失为一世伟人。玆非得是录于不可得之验欤。前后
写。以传诸子若孙。君其序焉。余以不文辞者屡而请益恳。不得已因其言。聊序其失与得之梗槩如右。又以语系其下曰。录之成在庚子。至丙辰七十有七年。自丙辰至乙丑七十年也。百四十馀年间。两失而两得之。其失其得。谁使然也。于初之失。飘转于湖之境而企村得之。于后之失。远在于鲸海万里之外而吾子得之。失而得之。其亦有待。子知其所以得者乎。吾以一录之得失。卜宋氏之兴衰何者。当其一失也。衰而企村显而得。及其再失也。不可谓之衰。而视企村则亦可谓之衰矣。子姓非一。其得在子。复老松之业而昌大之。其在子之家乎。潇洒翁得之于南原老儒。郑上舍得之于日本僧。在南原者或可得。在日本者不可得。然则企村之得。得之于或可得。吾子之得。得之于不可得。得亦有异哉。呜呼。凡代大家其兴有本。老松乘不测之舟。入豺虎之吻。竟完璧而归。录中诸什。盖公之事。匪本曷因。知所本而无倦无隳者企村是也。今子以企村之行于身者。常勉于子之身。而亦以是教诸子。所谓本者是在。而生于子之家者皆企村。自外轩冕。虽欲辞当自至矣。不幸而不至焉。亦不失为一世伟人。玆非得是录于不可得之验欤。前后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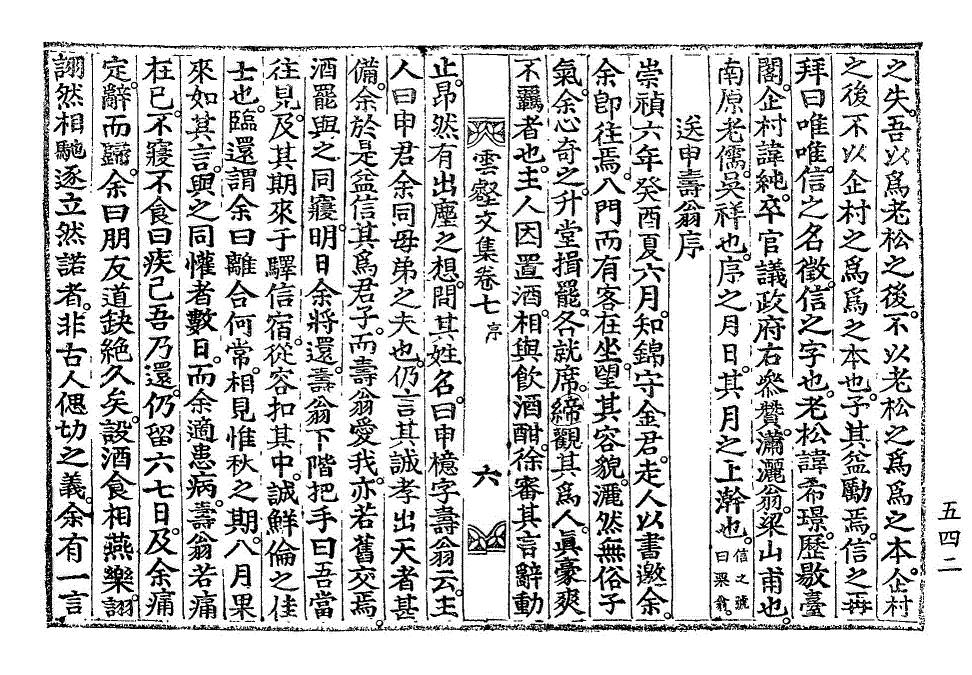 之失。吾以为老松之后。不以老松之为为之本。企村之后不以企村之为为之本也。子其益励焉。信之再拜曰唯唯。信之名徵。信之字也。老松讳希璟。历扬台阁。企村讳纯。卒官议政府右参赞。潇洒翁。梁山甫也。南原老儒。吴祥也。序之月日。其月之上浣也。(信之号曰栗翁。)
之失。吾以为老松之后。不以老松之为为之本。企村之后不以企村之为为之本也。子其益励焉。信之再拜曰唯唯。信之名徵。信之字也。老松讳希璟。历扬台阁。企村讳纯。卒官议政府右参赞。潇洒翁。梁山甫也。南原老儒。吴祥也。序之月日。其月之上浣也。(信之号曰栗翁。)送申寿翁序
崇祯六年癸酉夏六月。知锦守金君。走人以书邀余。余即往焉。入门而有客在坐。望其容貌。洒然无俗子气。余心奇之。升堂揖罢。各就席。缔观其为人。真豪爽不羁者也。主人因置酒。相与饮酒酣。徐审其言辞动止。昂然有出尘之想。问其姓名。曰申檍字寿翁云。主人曰申君余同母弟之夫也。仍言其诚孝出天者甚备。余于是益信其为君子。而寿翁爱我。亦若旧交焉。酒罢与之同寝。明日余将还。寿翁下阶把手曰吾当往见。及其期来于驿信宿。从容扣其中。诚鲜伦之佳士也。临还谓余曰离合何常。相见惟秋之期。八月果来如其言。与之同欢者数日。而余适患病。寿翁若痛在己。不寝不食曰疾已吾乃还。仍留六七日。及余痛定。辞而归。余曰朋友道缺绝久矣。设酒食相燕乐。诩诩然相驰逐立然诺者。非古人偲切之义。余有一言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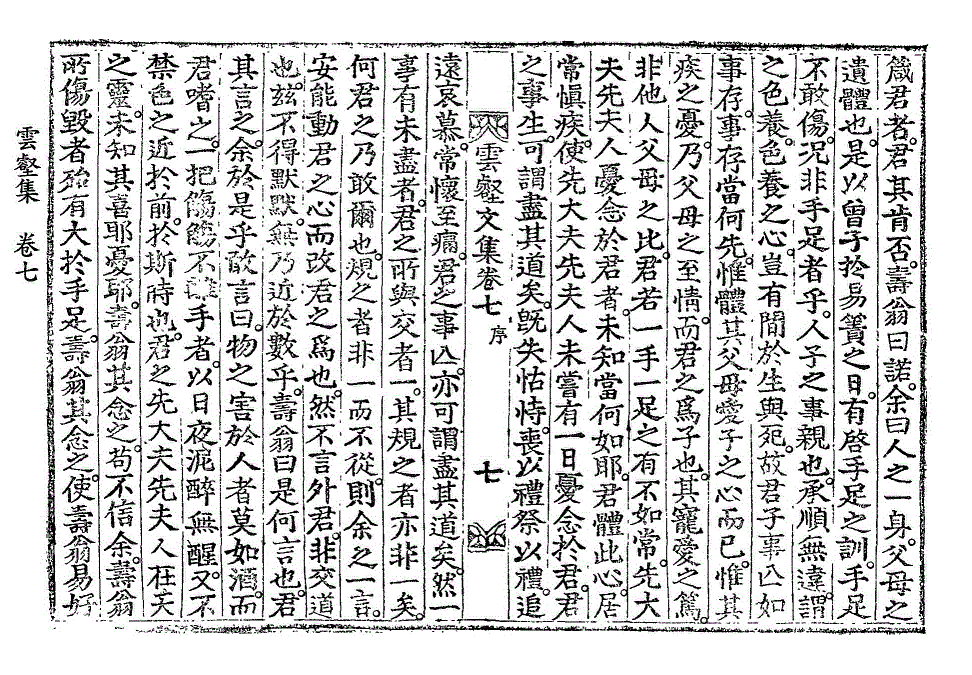 箴君者。君其肯否。寿翁曰诺。余曰人之一身。父母之遗体也。是以曾子于易箦之日。有启手足之训。手足不敢伤。况非手足者乎。人子之事亲也。承顺无违。谓之色养。色养之心。岂有间于生与死。故君子事亡如事存。事存当何先。惟体其父母爱子之心而已。惟其疾之忧。乃父母之至情。而君之为子也。其宠爱之笃。非他人父母之比。君若一手一足之有不如常。先大夫先夫人忧念于君者。未知当何如耶。君体此心。居常慎疾。使先大夫先夫人未尝有一日忧念于君。君之事生。可谓尽其道矣。既失怙恃。丧以礼祭以礼。追远哀慕。常怀至痛。君之事亡。亦可谓尽其道矣。然一事有未尽者。君之所与交者一。其规之者亦非一矣。何君之乃敢尔也。规之者非一而不从。则余之一言。安能动君之心而改君之为也。然不言外君。非交道也。玆不得默默。无乃近于数乎。寿翁曰是何言也。君其言之。余于是乎敢言曰。物之害于人者莫如酒。而君嗜之。一把觞觞不离手者。以日夜泥醉无醒。又不禁色之近于前。于斯时也。君之先大夫先夫人在天之灵。未知其喜耶忧耶。寿翁其念之。苟不信余。寿翁所伤毁者殆有大于手足。寿翁其念之。使寿翁易好
箴君者。君其肯否。寿翁曰诺。余曰人之一身。父母之遗体也。是以曾子于易箦之日。有启手足之训。手足不敢伤。况非手足者乎。人子之事亲也。承顺无违。谓之色养。色养之心。岂有间于生与死。故君子事亡如事存。事存当何先。惟体其父母爱子之心而已。惟其疾之忧。乃父母之至情。而君之为子也。其宠爱之笃。非他人父母之比。君若一手一足之有不如常。先大夫先夫人忧念于君者。未知当何如耶。君体此心。居常慎疾。使先大夫先夫人未尝有一日忧念于君。君之事生。可谓尽其道矣。既失怙恃。丧以礼祭以礼。追远哀慕。常怀至痛。君之事亡。亦可谓尽其道矣。然一事有未尽者。君之所与交者一。其规之者亦非一矣。何君之乃敢尔也。规之者非一而不从。则余之一言。安能动君之心而改君之为也。然不言外君。非交道也。玆不得默默。无乃近于数乎。寿翁曰是何言也。君其言之。余于是乎敢言曰。物之害于人者莫如酒。而君嗜之。一把觞觞不离手者。以日夜泥醉无醒。又不禁色之近于前。于斯时也。君之先大夫先夫人在天之灵。未知其喜耶忧耶。寿翁其念之。苟不信余。寿翁所伤毁者殆有大于手足。寿翁其念之。使寿翁易好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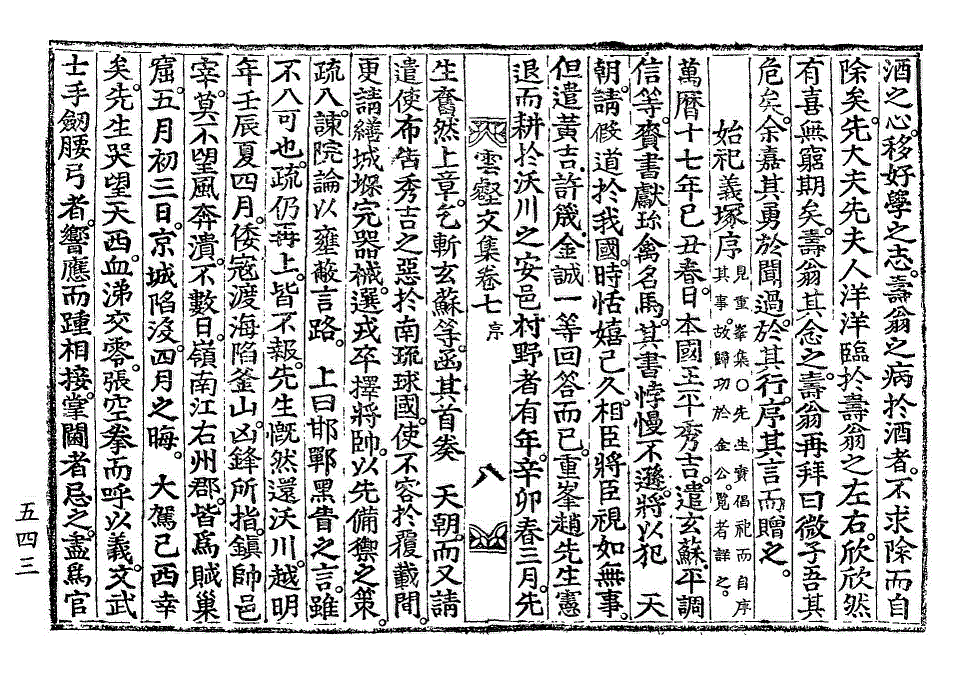 酒之心。移好学之志。寿翁之病于酒者。不求除而自除矣。先大夫先夫人洋洋临于寿翁之左右。欣欣然有喜无穷期矣。寿翁其念之。寿翁再拜曰微子吾其危矣。余嘉其勇于闻过。于其行。序其言而赠之。
酒之心。移好学之志。寿翁之病于酒者。不求除而自除矣。先大夫先夫人洋洋临于寿翁之左右。欣欣然有喜无穷期矣。寿翁其念之。寿翁再拜曰微子吾其危矣。余嘉其勇于闻过。于其行。序其言而赠之。始祀义冢序(见重峰集○先生实倡祀而自序其事。故归功于金公。览者详之。)
万历十七年己丑春。日本国王平秀吉。遣玄苏,平调信等。赉书献珍禽名马。其书悖慢不逊。将以犯 天朝。请假道于我国。时恬嬉已久。相臣将臣视如无事。但遣黄吉,许筬,金诚一等回答而已。重峰赵先生宪退而耕于沃川之安邑村野者有年。辛卯春三月。先生奋然上章。乞斩玄苏等。函其首奏 天朝。而又请遣使布告秀吉之恶于南琉球国。使不容于覆载间。更请缮城堢完器械。选戎卒择将帅。以先备御之策。疏入。谏院论以壅蔽言路。 上曰邯郸黑眚之言。虽不入可也。疏仍再上。皆不报。先生慨然还沃川。越明年壬辰夏四月。倭寇渡海陷釜山。凶锋所指。镇帅邑宰。莫不望风奔溃。不数日。岭南江右州郡。皆为贼巢窟。五月初三日。京城陷没。四月之晦。 大驾已西幸矣。先生哭望天西。血涕交零。张空拳而呼以义。文武士手剑腰弓者。响应而踵相接。掌阃者忌之。尽为官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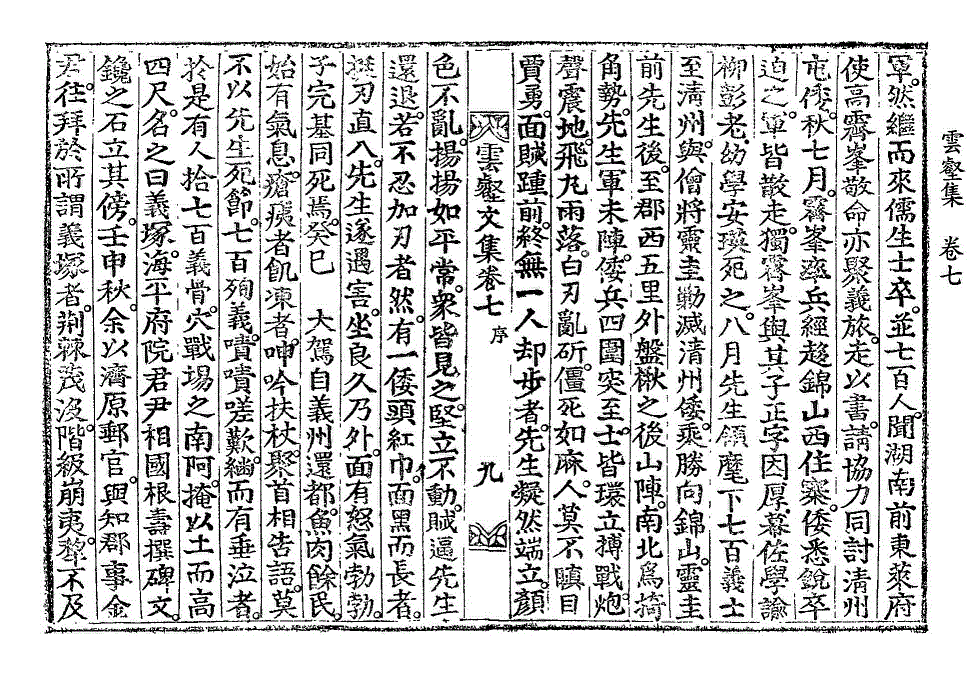 军。然继而来儒生士卒。并七百人。闻湖南前东莱府使高霁峰敬命亦聚义旅。走以书。请协力同讨清州屯倭。秋七月。霁峰率兵经趍锦山西住寨。倭悉锐卒迫之。军皆散走。独霁峰与其子正字因厚,幕佐学谕柳彭老,幼学安瑛死之。八月先生领麾下七百义士至清州。与僧将灵圭剿灭清州倭。乘胜向锦山。灵圭前先生后。至郡西五里外盘楸之后山阵。南北为掎角势。先生军未阵。倭兵四围突至。士皆环立搏战。炮声震地。飞丸雨落。白刃乱斫。僵死如麻。人莫不瞋目贾勇。面贼踵前。终无一人却步者。先生凝然端立。颜色不乱。扬扬如平常。众皆见之。坚立不动。贼逼先生还退。若不忍加刃者然。有一倭头红巾。面黑而长者。挺刃直入。先生遂遇害。坐良久乃外。面有怒气勃勃。子完基同死焉。癸巳 大驾自义州还都。鱼肉馀民。始有气息。疮痍者饥冻者。呻吟扶杖。聚首相告语。莫不以先生死节。七百殉义。啧啧嗟叹。继而有垂泣者。于是有人拾七百义骨。穴战场之南阿。掩以土而高四尺。名之曰义冢。海平府院君尹相国根寿撰碑文。镵之石立其傍。壬申秋。余以济原邮官。与知郡事金君。往拜于所谓义冢者。荆棘茂没。阶级崩夷。犁不及
军。然继而来儒生士卒。并七百人。闻湖南前东莱府使高霁峰敬命亦聚义旅。走以书。请协力同讨清州屯倭。秋七月。霁峰率兵经趍锦山西住寨。倭悉锐卒迫之。军皆散走。独霁峰与其子正字因厚,幕佐学谕柳彭老,幼学安瑛死之。八月先生领麾下七百义士至清州。与僧将灵圭剿灭清州倭。乘胜向锦山。灵圭前先生后。至郡西五里外盘楸之后山阵。南北为掎角势。先生军未阵。倭兵四围突至。士皆环立搏战。炮声震地。飞丸雨落。白刃乱斫。僵死如麻。人莫不瞋目贾勇。面贼踵前。终无一人却步者。先生凝然端立。颜色不乱。扬扬如平常。众皆见之。坚立不动。贼逼先生还退。若不忍加刃者然。有一倭头红巾。面黑而长者。挺刃直入。先生遂遇害。坐良久乃外。面有怒气勃勃。子完基同死焉。癸巳 大驾自义州还都。鱼肉馀民。始有气息。疮痍者饥冻者。呻吟扶杖。聚首相告语。莫不以先生死节。七百殉义。啧啧嗟叹。继而有垂泣者。于是有人拾七百义骨。穴战场之南阿。掩以土而高四尺。名之曰义冢。海平府院君尹相国根寿撰碑文。镵之石立其傍。壬申秋。余以济原邮官。与知郡事金君。往拜于所谓义冢者。荆棘茂没。阶级崩夷。犁不及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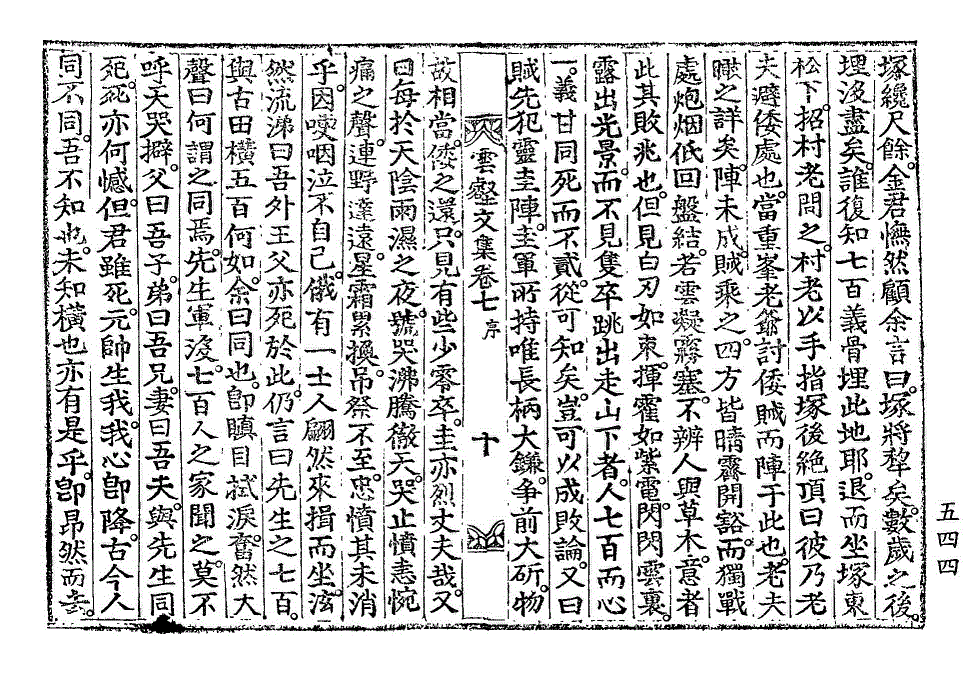 冢才尺馀。金君怃然顾余言曰。冢将犁矣。数岁之后。埋没尽矣。谁复知七百义骨埋此地耶。退而坐冢东松下。招村老问之。村老以手指冢后绝顶曰彼乃老夫避倭处也。当重峰老爷讨倭贼而阵于此也。老夫瞰之详矣。阵未成。贼乘之。四方皆晴霁开豁。而独战处炮烟低回盘结。若云凝雾塞。不辨人与草木。意者此其败兆也。但见白刃如束。挥霍如紫电。闪闪云里。露出光景。而不见只卒跳出走山下者。人七百而心一。义甘同死而不贰。从可知矣。岂可以成败论。又曰贼先犯灵圭阵。圭军所持唯长柄大镰。争前大斫。物故相当。倭之还。只见有些少零卒。圭亦烈丈夫哉。又曰每于天阴雨湿之夜。号哭沸腾彻天。哭止愤恚惋痛之声。连野达远。星霜累换。吊祭不至。忠愤其未消乎。因哽咽泣不自已。俄有一士人翩然来揖而坐。泫然流涕曰吾外王父亦死于此。仍言曰先生之七百。与古田横五百何如。余曰同也。即瞋目拭泪。奋然大声曰何谓之同焉。先生军没。七百人之家闻之。莫不呼天哭擗。父曰吾子。弟曰吾兄。妻曰吾夫。与先生同死。死亦何憾。但君虽死。元帅生我。我心即降。古今人同不同。吾不知也。未知横也亦有是乎。即昂然而去。
冢才尺馀。金君怃然顾余言曰。冢将犁矣。数岁之后。埋没尽矣。谁复知七百义骨埋此地耶。退而坐冢东松下。招村老问之。村老以手指冢后绝顶曰彼乃老夫避倭处也。当重峰老爷讨倭贼而阵于此也。老夫瞰之详矣。阵未成。贼乘之。四方皆晴霁开豁。而独战处炮烟低回盘结。若云凝雾塞。不辨人与草木。意者此其败兆也。但见白刃如束。挥霍如紫电。闪闪云里。露出光景。而不见只卒跳出走山下者。人七百而心一。义甘同死而不贰。从可知矣。岂可以成败论。又曰贼先犯灵圭阵。圭军所持唯长柄大镰。争前大斫。物故相当。倭之还。只见有些少零卒。圭亦烈丈夫哉。又曰每于天阴雨湿之夜。号哭沸腾彻天。哭止愤恚惋痛之声。连野达远。星霜累换。吊祭不至。忠愤其未消乎。因哽咽泣不自已。俄有一士人翩然来揖而坐。泫然流涕曰吾外王父亦死于此。仍言曰先生之七百。与古田横五百何如。余曰同也。即瞋目拭泪。奋然大声曰何谓之同焉。先生军没。七百人之家闻之。莫不呼天哭擗。父曰吾子。弟曰吾兄。妻曰吾夫。与先生同死。死亦何憾。但君虽死。元帅生我。我心即降。古今人同不同。吾不知也。未知横也亦有是乎。即昂然而去。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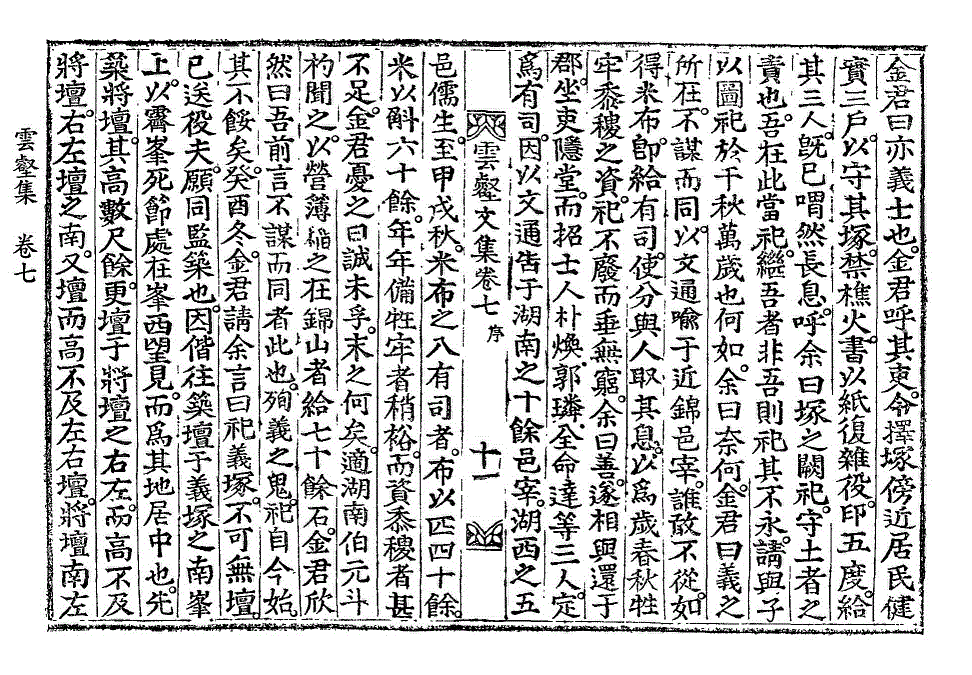 金君曰亦义士也。金君呼其吏。令择冢傍近居民健实三户。以守其冢。禁樵火。书以纸复杂役。印五度。给其三人。既已喟然长息。呼余曰冢之阙祀。守土者之责也。吾在此当祀。继吾者非吾则祀其不永。请与子以图祀于千秋万岁也何如。余曰奈何。金君曰义之所在。不谋而同。以文通喻于近锦邑宰。谁敢不从。如得米布。即给有司。使分与人取其息。以为岁春秋牲牢黍稷之资。祀不废而垂无穷。余曰善。遂相与还于郡。坐吏隐堂。而招士人朴焕,郭璘,全命达等三人。定为有司。因以文通告于湖南之十馀邑宰。湖西之五邑儒生。至甲戌秋。米布之入有司者。布以匹四十馀。米以斛六十馀。年年备牲牢者稍裕。而资黍稷者甚不足。金君忧之曰诚未孚。末之何矣。适湖南伯元斗杓闻之。以营簿稻之在锦山者给七十馀石。金君欣然曰吾前言不谋而同者此也。殉义之鬼。祀自今始。其不馁矣。癸酉冬。金君请余言曰祀义冢。不可无坛。已送役夫。愿同监筑也。因偕往筑坛于义冢之南峰上。以霁峰死节处在峰西望见。而为其地居中也。先筑将坛。其高数尺馀。更坛于将坛之右左。而高不及将坛。右左坛之南。又坛而高不及左右坛。将坛南左
金君曰亦义士也。金君呼其吏。令择冢傍近居民健实三户。以守其冢。禁樵火。书以纸复杂役。印五度。给其三人。既已喟然长息。呼余曰冢之阙祀。守土者之责也。吾在此当祀。继吾者非吾则祀其不永。请与子以图祀于千秋万岁也何如。余曰奈何。金君曰义之所在。不谋而同。以文通喻于近锦邑宰。谁敢不从。如得米布。即给有司。使分与人取其息。以为岁春秋牲牢黍稷之资。祀不废而垂无穷。余曰善。遂相与还于郡。坐吏隐堂。而招士人朴焕,郭璘,全命达等三人。定为有司。因以文通告于湖南之十馀邑宰。湖西之五邑儒生。至甲戌秋。米布之入有司者。布以匹四十馀。米以斛六十馀。年年备牲牢者稍裕。而资黍稷者甚不足。金君忧之曰诚未孚。末之何矣。适湖南伯元斗杓闻之。以营簿稻之在锦山者给七十馀石。金君欣然曰吾前言不谋而同者此也。殉义之鬼。祀自今始。其不馁矣。癸酉冬。金君请余言曰祀义冢。不可无坛。已送役夫。愿同监筑也。因偕往筑坛于义冢之南峰上。以霁峰死节处在峰西望见。而为其地居中也。先筑将坛。其高数尺馀。更坛于将坛之右左。而高不及将坛。右左坛之南。又坛而高不及左右坛。将坛南左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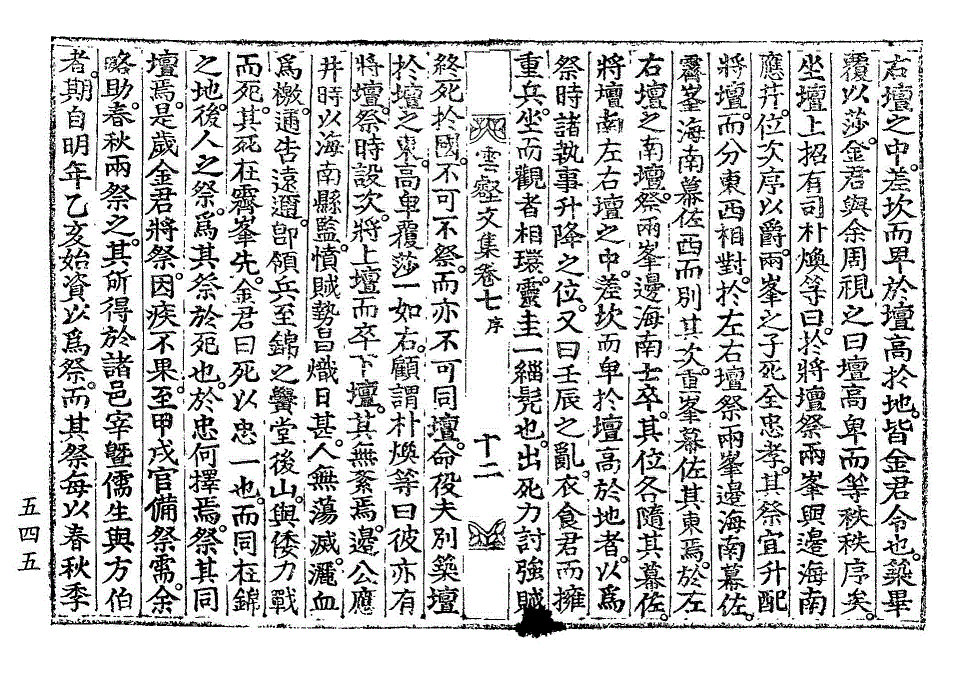 右坛之中。差坎而卑于坛高于地。皆金君令也。筑毕覆以莎。金君与余周视之曰坛高卑而等秩秩序矣。坐坛上招有司朴焕等曰。于将坛祭两峰与边海南应井。位次序以爵。两峰之子死全忠孝。其祭宜升配将坛。而分东西相对。于左右坛祭两峰边海南幕佐。霁峰海南幕佐西而别其次。重峰幕佐其东焉。于左右坛之南坛。祭两峰边海南士卒。其位各随其幕佐。将坛南左右坛之中。差坎而卑于坛高于地者。以为祭时诸执事升降之位。又曰壬辰之乱。衣食君而拥重兵。坐而观者相环。灵圭一缁髡也。出死力讨强贼。终死于国。不可不祭。而亦不可同坛。命役夫别筑坛于坛之东。高卑覆莎一如右。顾谓朴焕等曰彼亦有将坛。祭时设次。将上坛而卒下坛。其无紊焉。边公应井时以海南县监。愤贼势昌炽日甚。人无荡灭。洒血为檄。通告远迩。即领兵至锦之黉堂后山。与倭力战而死。其死在霁峰先。金君曰死以忠一也。而同在锦之地。后人之祭。为其祭于死也。于忠何择焉。祭其同坛焉。是岁金君将祭。因疾不果。至甲戌官备祭需。余略助。春秋两祭之。其所得于诸邑宰暨儒生与方伯者。期自明年乙亥始资以为祭。而其祭每以春秋季
右坛之中。差坎而卑于坛高于地。皆金君令也。筑毕覆以莎。金君与余周视之曰坛高卑而等秩秩序矣。坐坛上招有司朴焕等曰。于将坛祭两峰与边海南应井。位次序以爵。两峰之子死全忠孝。其祭宜升配将坛。而分东西相对。于左右坛祭两峰边海南幕佐。霁峰海南幕佐西而别其次。重峰幕佐其东焉。于左右坛之南坛。祭两峰边海南士卒。其位各随其幕佐。将坛南左右坛之中。差坎而卑于坛高于地者。以为祭时诸执事升降之位。又曰壬辰之乱。衣食君而拥重兵。坐而观者相环。灵圭一缁髡也。出死力讨强贼。终死于国。不可不祭。而亦不可同坛。命役夫别筑坛于坛之东。高卑覆莎一如右。顾谓朴焕等曰彼亦有将坛。祭时设次。将上坛而卒下坛。其无紊焉。边公应井时以海南县监。愤贼势昌炽日甚。人无荡灭。洒血为檄。通告远迩。即领兵至锦之黉堂后山。与倭力战而死。其死在霁峰先。金君曰死以忠一也。而同在锦之地。后人之祭。为其祭于死也。于忠何择焉。祭其同坛焉。是岁金君将祭。因疾不果。至甲戌官备祭需。余略助。春秋两祭之。其所得于诸邑宰暨儒生与方伯者。期自明年乙亥始资以为祭。而其祭每以春秋季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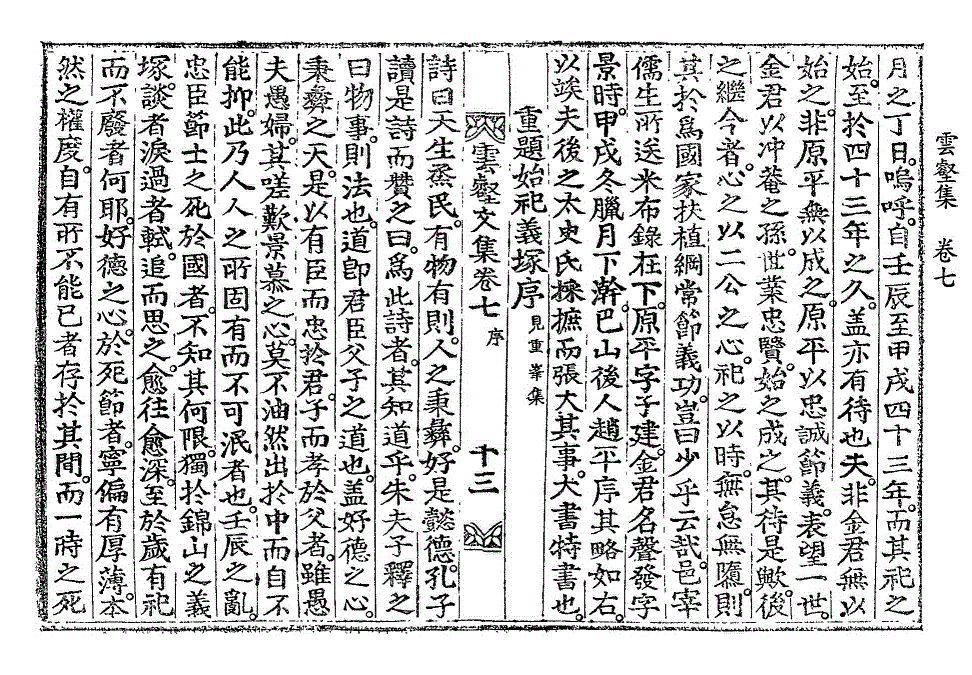 月之丁日。呜呼。自壬辰至甲戌四十三年。而其祀之始。至于四十三年之久。盖亦有待也夫。非金君无以始之。非原平无以成之。原平以忠诚节义。表望一世。金君以冲庵之孙。世业忠贤。始之成之。其待是欤。后之继今者。心之以二公之心。祀之以时。无怠无隳。则其于为国家扶植纲常节义功。岂曰少乎云哉。邑宰儒生所送米布录在下。原平字子建。金君名声发字景时。甲戌冬腊月下浣。巴山后人赵平序其略如右。以俟夫后之太史氏采摭而张大其事。大书特书也。
月之丁日。呜呼。自壬辰至甲戌四十三年。而其祀之始。至于四十三年之久。盖亦有待也夫。非金君无以始之。非原平无以成之。原平以忠诚节义。表望一世。金君以冲庵之孙。世业忠贤。始之成之。其待是欤。后之继今者。心之以二公之心。祀之以时。无怠无隳。则其于为国家扶植纲常节义功。岂曰少乎云哉。邑宰儒生所送米布录在下。原平字子建。金君名声发字景时。甲戌冬腊月下浣。巴山后人赵平序其略如右。以俟夫后之太史氏采摭而张大其事。大书特书也。重题始祀义冢序(见重峰集)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读是诗而赞之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朱夫子释之曰物事。则法也。道即君臣父子之道也。盖好德之心。秉彝之天。是以有臣而忠于君。子而孝于父者。虽愚夫愚妇。其嗟叹景慕之心。莫不油然出于中而自不能抑。此乃人人之所固有而不可泯者也。壬辰之乱。忠臣节士之死于国者。不知其何限。独于锦山之义冢。谈者泪过者轼。追而思之。愈往愈深。至于岁有祀而不废者何耶。好德之心。于死节者。宁偏有厚薄。本然之权度。自有所不能已者存于其间。而一时之死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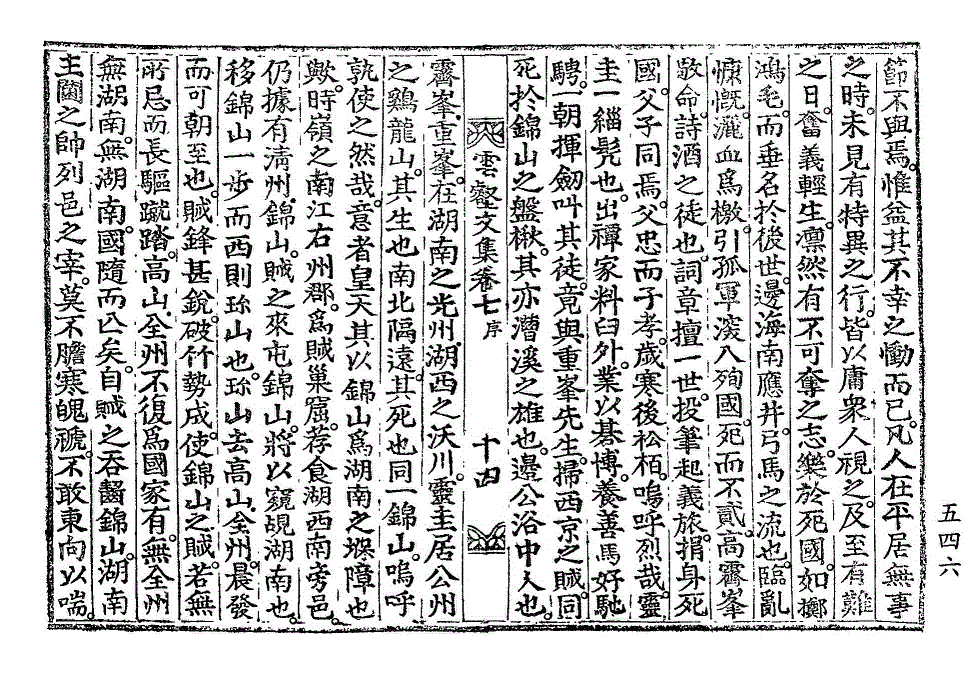 节不与焉。惟益其不幸之恸而已。凡人在平居无事之时。未见有特异之行。皆以庸众人视之。及至有难之日。奋义轻生。凛然有不可夺之志。乐于死国。如掷鸿毛。而垂名于后世。边海南应井。弓马之流也。临乱慷慨。洒血为檄。引孤军深入殉国。死而不贰。高霁峰敬命。诗酒之徒也。词章擅一世。投笔起义旅。捐身死国。父子同焉。父忠而子孝。岁寒后松柏。呜呼烈哉。灵圭一缁髡也。出禫家料臼外。业以棋博。养善马好驰骋。一朝挥剑叫其徒。竟与重峰先生。扫西京之贼。同死于锦山之盘楸。其亦漕溪之雄也。边公浴中人也。霁峰,重峰。在湖南之光州,湖西之沃川。灵圭居公州之鸡龙山。其生也南北隔远。其死也同一锦山。呜呼孰使之然哉。意者皇天其以锦山为湖南之堢障也欤。时岭之南江右州郡。为贼巢窟。荐食湖西南旁邑。仍据有清州,锦山。贼之来屯锦山。将以窥觇湖南也。移锦山一步而西则珍山也。珍山去高山,全州。晨发而可朝至也。贼锋甚锐。破竹势成。使锦山之贼。若无所忌而长驱蹴踏。高山,全州不复为国家有。无全州无湖南。无湖南。国随而亡矣。自贼之吞齧锦山。湖南主阃之帅列邑之宰。莫不胆寒魄褫。不敢东向以喘。
节不与焉。惟益其不幸之恸而已。凡人在平居无事之时。未见有特异之行。皆以庸众人视之。及至有难之日。奋义轻生。凛然有不可夺之志。乐于死国。如掷鸿毛。而垂名于后世。边海南应井。弓马之流也。临乱慷慨。洒血为檄。引孤军深入殉国。死而不贰。高霁峰敬命。诗酒之徒也。词章擅一世。投笔起义旅。捐身死国。父子同焉。父忠而子孝。岁寒后松柏。呜呼烈哉。灵圭一缁髡也。出禫家料臼外。业以棋博。养善马好驰骋。一朝挥剑叫其徒。竟与重峰先生。扫西京之贼。同死于锦山之盘楸。其亦漕溪之雄也。边公浴中人也。霁峰,重峰。在湖南之光州,湖西之沃川。灵圭居公州之鸡龙山。其生也南北隔远。其死也同一锦山。呜呼孰使之然哉。意者皇天其以锦山为湖南之堢障也欤。时岭之南江右州郡。为贼巢窟。荐食湖西南旁邑。仍据有清州,锦山。贼之来屯锦山。将以窥觇湖南也。移锦山一步而西则珍山也。珍山去高山,全州。晨发而可朝至也。贼锋甚锐。破竹势成。使锦山之贼。若无所忌而长驱蹴踏。高山,全州不复为国家有。无全州无湖南。无湖南。国随而亡矣。自贼之吞齧锦山。湖南主阃之帅列邑之宰。莫不胆寒魄褫。不敢东向以喘。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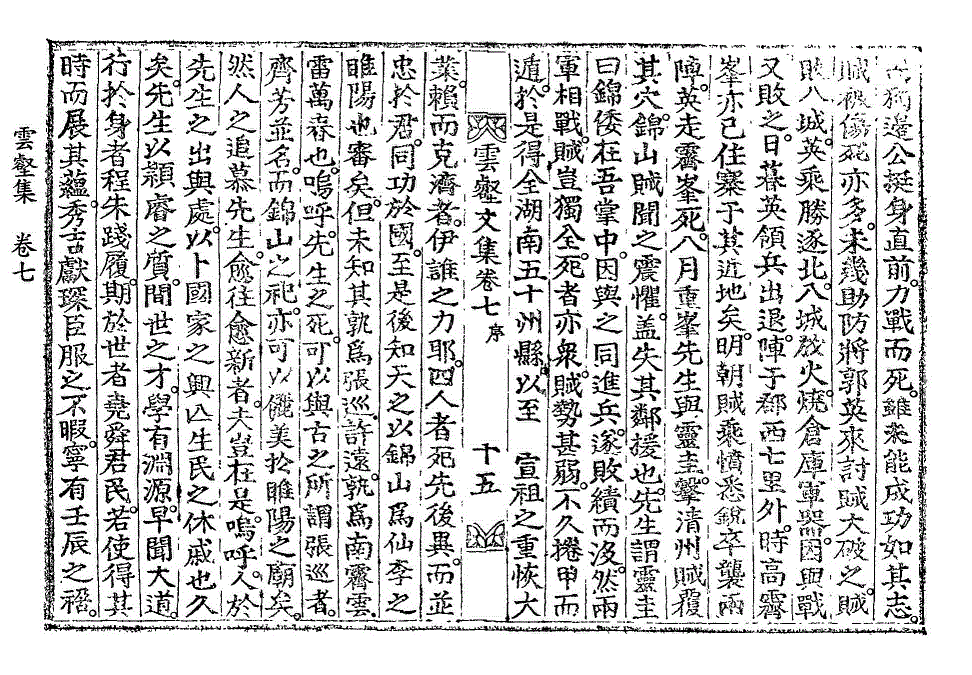 而独边公挺身直前。力战而死。虽未能成功如其志。贼被伤死亦多。未几助防将郭英来讨贼大破之。贼败入城。英乘胜逐北。入城放火。烧仓库军器。因与战又败之。日暮英领兵出退。阵于郡西七里外。时高霁峰亦已住寨于其近地矣。明朝贼乘愤悉锐卒袭两阵。英走霁峰死。八月重峰先生与灵圭。击清州贼覆其穴。锦山贼闻之震惧。盖失其邻援也。先生谓灵圭曰锦倭在吾掌中。因与之同进兵。遂败绩而没。然两军相战。贼岂独全。死者亦众。贼势甚弱。不久捲甲而遁。于是得全湖南五十州县。以至 宣祖之重恢大业。赖而克济者。伊谁之力耶。四人者死先后异。而并忠于君。同功于国。至是后知天之以锦山为仙李之睢阳也审矣。但未知其孰为张巡,许远。孰为南霁云,雷万春也。呜呼。先生之死。可以与古之所谓张巡者。齐芳并名。而锦山之祀。亦可以俪美于睢阳之庙矣。然人之追慕先生。愈往愈新者。夫岂在是。呜呼。人于先生之出与处。以卜国家之兴亡生民之休戚也久矣。先生以颖睿之质。间世之才。学有渊源。早闻大道。行于身者程朱践履。期于世者尧舜君民。若使得其时而展其蕴。秀吉献琛臣服之不暇。宁有壬辰之𥚁。
而独边公挺身直前。力战而死。虽未能成功如其志。贼被伤死亦多。未几助防将郭英来讨贼大破之。贼败入城。英乘胜逐北。入城放火。烧仓库军器。因与战又败之。日暮英领兵出退。阵于郡西七里外。时高霁峰亦已住寨于其近地矣。明朝贼乘愤悉锐卒袭两阵。英走霁峰死。八月重峰先生与灵圭。击清州贼覆其穴。锦山贼闻之震惧。盖失其邻援也。先生谓灵圭曰锦倭在吾掌中。因与之同进兵。遂败绩而没。然两军相战。贼岂独全。死者亦众。贼势甚弱。不久捲甲而遁。于是得全湖南五十州县。以至 宣祖之重恢大业。赖而克济者。伊谁之力耶。四人者死先后异。而并忠于君。同功于国。至是后知天之以锦山为仙李之睢阳也审矣。但未知其孰为张巡,许远。孰为南霁云,雷万春也。呜呼。先生之死。可以与古之所谓张巡者。齐芳并名。而锦山之祀。亦可以俪美于睢阳之庙矣。然人之追慕先生。愈往愈新者。夫岂在是。呜呼。人于先生之出与处。以卜国家之兴亡生民之休戚也久矣。先生以颖睿之质。间世之才。学有渊源。早闻大道。行于身者程朱践履。期于世者尧舜君民。若使得其时而展其蕴。秀吉献琛臣服之不暇。宁有壬辰之𥚁。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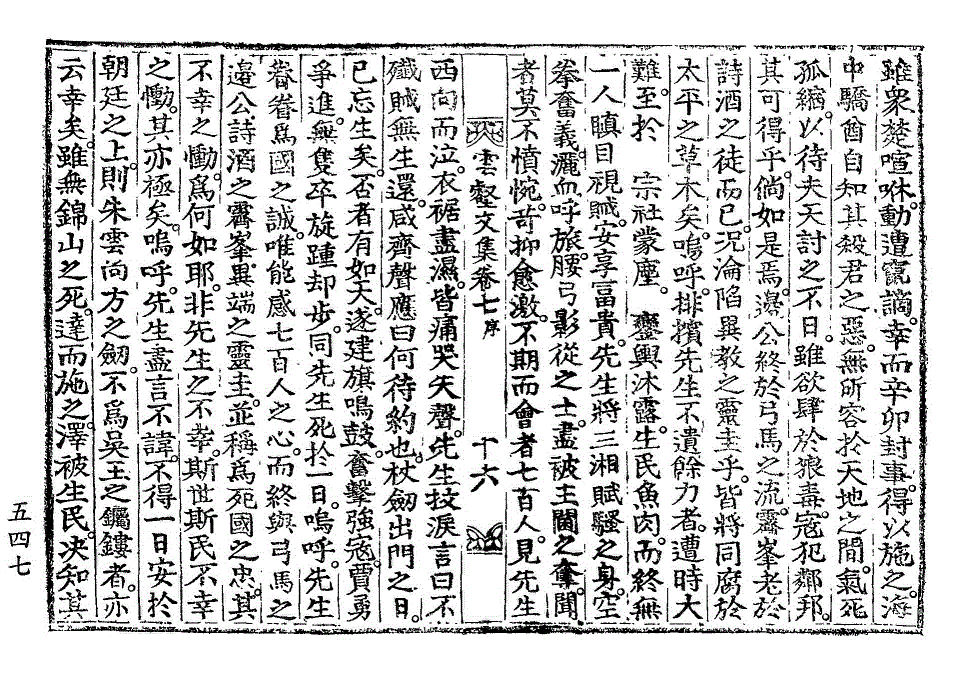 虽众楚喧咻。动遭窜谪。幸而辛卯封事。得以施之。海中骄酋自知其杀君之恶。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气死孤缩。以待夫天讨之不日。虽欲肆于狼毒。寇犯邻邦。其可得乎。倘如是焉。边公终于弓马之流。霁峰老于诗酒之徒而已。况沦陷异教之灵圭乎。皆将同腐于太平之草木矣。呜呼。排摈先生不遗馀力者。遭时大难。至于 宗社蒙尘。 銮舆沐露。生民鱼肉。而终无一人瞋目视贼。安享富贵。先生将三湘赋骚之身。空拳奋义。洒血呼旅。腰弓影从之士。尽被主阃之夺。闻者莫不愤惋。苛抑愈激。不期而会者七百人。见先生西向而泣。衣裾尽湿。皆痛哭失声。先生抆泪言曰不歼贼无生还。咸齐声应曰何待约也。杖剑出门之日。已忘生矣。否者有如天。遂建旗鸣鼓。奋击强寇。贾勇争进。无只卒旋踵却步。同先生死于一日。呜呼。先生眷眷为国之诚。唯能感七百人之心。而终与弓马之边公,诗酒之霁峰,异端之灵圭。并称为死国之忠。其不幸之恸。为何如耶。非先生之不幸。斯世斯民不幸之恸。其亦极矣。呜呼。先生尽言不讳。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则朱云尚方之剑。不为吴王之钃镂者。亦云幸矣。虽无锦山之死。达而施之。泽被生民。决知其
虽众楚喧咻。动遭窜谪。幸而辛卯封事。得以施之。海中骄酋自知其杀君之恶。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气死孤缩。以待夫天讨之不日。虽欲肆于狼毒。寇犯邻邦。其可得乎。倘如是焉。边公终于弓马之流。霁峰老于诗酒之徒而已。况沦陷异教之灵圭乎。皆将同腐于太平之草木矣。呜呼。排摈先生不遗馀力者。遭时大难。至于 宗社蒙尘。 銮舆沐露。生民鱼肉。而终无一人瞋目视贼。安享富贵。先生将三湘赋骚之身。空拳奋义。洒血呼旅。腰弓影从之士。尽被主阃之夺。闻者莫不愤惋。苛抑愈激。不期而会者七百人。见先生西向而泣。衣裾尽湿。皆痛哭失声。先生抆泪言曰不歼贼无生还。咸齐声应曰何待约也。杖剑出门之日。已忘生矣。否者有如天。遂建旗鸣鼓。奋击强寇。贾勇争进。无只卒旋踵却步。同先生死于一日。呜呼。先生眷眷为国之诚。唯能感七百人之心。而终与弓马之边公,诗酒之霁峰,异端之灵圭。并称为死国之忠。其不幸之恸。为何如耶。非先生之不幸。斯世斯民不幸之恸。其亦极矣。呜呼。先生尽言不讳。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则朱云尚方之剑。不为吴王之钃镂者。亦云幸矣。虽无锦山之死。达而施之。泽被生民。决知其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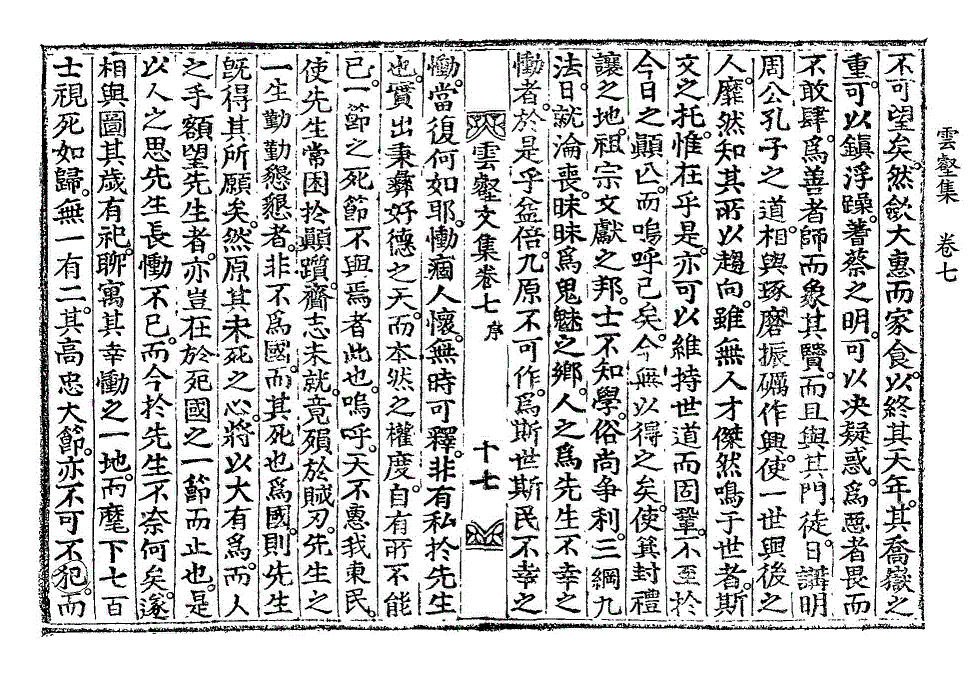 不可望矣。然敛大惠而家食。以终其天年。其乔岳之重。可以镇浮躁。蓍蔡之明。可以决疑惑。为恶者畏而不敢肆。为善者师而象其贤。而且与其门徒。日讲明周公孔子之道。相与琢磨振砺作兴。使一世与后之人。靡然知其所以趋向。虽无人才杰然鸣于世者。斯文之托。惟在乎是。亦可以维持世道而固巩。不至于今日之颠亡。而呜呼已矣。今无以得之矣。使箕封礼让之地。祖宗文献之邦。士不知学。俗尚争利。三纲九法。日就沦丧。昧昧为鬼魅之乡。人之为先生不幸之恸者。于是乎益倍。九原不可作。为斯世斯民不幸之恸。当复何如耶。恸痼人怀。无时可释。非有私于先生也。实出秉彝好德之天。而本然之权度。自有所不能已。一节之死节不与焉者此也。呜呼。天不惠我东民。使先生常困于颠踬。赍志未就。竟殒于贼刃。先生之一生勤勤恳恳者。非不为国。而其死也为国。则先生既得其所愿矣。然原其未死之心。将以大有为。而人之手额望先生者。亦岂在于死国之一节而止也。是以人之思先生长恸不已。而今于先生不奈何矣。遂相与图其岁有祀。聊寓其幸恸之一地。而麾下七百士视死如归。无一有二。其高忠大节。亦不可不犯。而
不可望矣。然敛大惠而家食。以终其天年。其乔岳之重。可以镇浮躁。蓍蔡之明。可以决疑惑。为恶者畏而不敢肆。为善者师而象其贤。而且与其门徒。日讲明周公孔子之道。相与琢磨振砺作兴。使一世与后之人。靡然知其所以趋向。虽无人才杰然鸣于世者。斯文之托。惟在乎是。亦可以维持世道而固巩。不至于今日之颠亡。而呜呼已矣。今无以得之矣。使箕封礼让之地。祖宗文献之邦。士不知学。俗尚争利。三纲九法。日就沦丧。昧昧为鬼魅之乡。人之为先生不幸之恸者。于是乎益倍。九原不可作。为斯世斯民不幸之恸。当复何如耶。恸痼人怀。无时可释。非有私于先生也。实出秉彝好德之天。而本然之权度。自有所不能已。一节之死节不与焉者此也。呜呼。天不惠我东民。使先生常困于颠踬。赍志未就。竟殒于贼刃。先生之一生勤勤恳恳者。非不为国。而其死也为国。则先生既得其所愿矣。然原其未死之心。将以大有为。而人之手额望先生者。亦岂在于死国之一节而止也。是以人之思先生长恸不已。而今于先生不奈何矣。遂相与图其岁有祀。聊寓其幸恸之一地。而麾下七百士视死如归。无一有二。其高忠大节。亦不可不犯。而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8L 页
 顾念边海南,高霁峰,灵圭之死。实有赖于重恢者。厥功甚钜。非死于陷摧数阵者之比。若有近于先生而不及焉。不但三人之名。泯没无传。窃恐同在锦地之忠魂。相与徘徊于坛侧。有后人莫我知之悲。故并祭之同其坛。先生不幸之恸。至此尤不禁其泪下矣。呜呼。同为是人则同为是心。闻龙蛇录中。有一战死者。射一贼杀一贼斩一贼者。莫不书其姓名邑居。同有是心之天。亦可谓不泯。而至于先生阙焉不书。详于彼而略于此。记其小而遣其大。其好恶予夺。一何颠错谬戾之至此哉。若曰先生所抱者大。而一时死节之忠。亘天地光日月。当赫人耳目。流声万世。吾所录录微。其将以显于后。则其亦可矣。如其不然。岂先生生时积憾忌嫉之心。快逞于一录之中欤。冰灰既殊。固不足多责。又有一宰相曲意著书。以先生之死。无所避逃。势出于不得已。乌可谓之忠节也。呜呼。鼎铛尚有耳。奈之何若不闻先生者然。而欲涂塞一时与后人之耳目也如此哉。反不如愚夫愚妇嗟叹景慕之自不能抑。岂皇天均赋秉彝之良。偏独啬于此人也耶。与先生生同世立同朝。待先生甚有礼意。倾诚倾情。以示其好善亲切之义。一世之人。虽稚童马卒。
顾念边海南,高霁峰,灵圭之死。实有赖于重恢者。厥功甚钜。非死于陷摧数阵者之比。若有近于先生而不及焉。不但三人之名。泯没无传。窃恐同在锦地之忠魂。相与徘徊于坛侧。有后人莫我知之悲。故并祭之同其坛。先生不幸之恸。至此尤不禁其泪下矣。呜呼。同为是人则同为是心。闻龙蛇录中。有一战死者。射一贼杀一贼斩一贼者。莫不书其姓名邑居。同有是心之天。亦可谓不泯。而至于先生阙焉不书。详于彼而略于此。记其小而遣其大。其好恶予夺。一何颠错谬戾之至此哉。若曰先生所抱者大。而一时死节之忠。亘天地光日月。当赫人耳目。流声万世。吾所录录微。其将以显于后。则其亦可矣。如其不然。岂先生生时积憾忌嫉之心。快逞于一录之中欤。冰灰既殊。固不足多责。又有一宰相曲意著书。以先生之死。无所避逃。势出于不得已。乌可谓之忠节也。呜呼。鼎铛尚有耳。奈之何若不闻先生者然。而欲涂塞一时与后人之耳目也如此哉。反不如愚夫愚妇嗟叹景慕之自不能抑。岂皇天均赋秉彝之良。偏独啬于此人也耶。与先生生同世立同朝。待先生甚有礼意。倾诚倾情。以示其好善亲切之义。一世之人。虽稚童马卒。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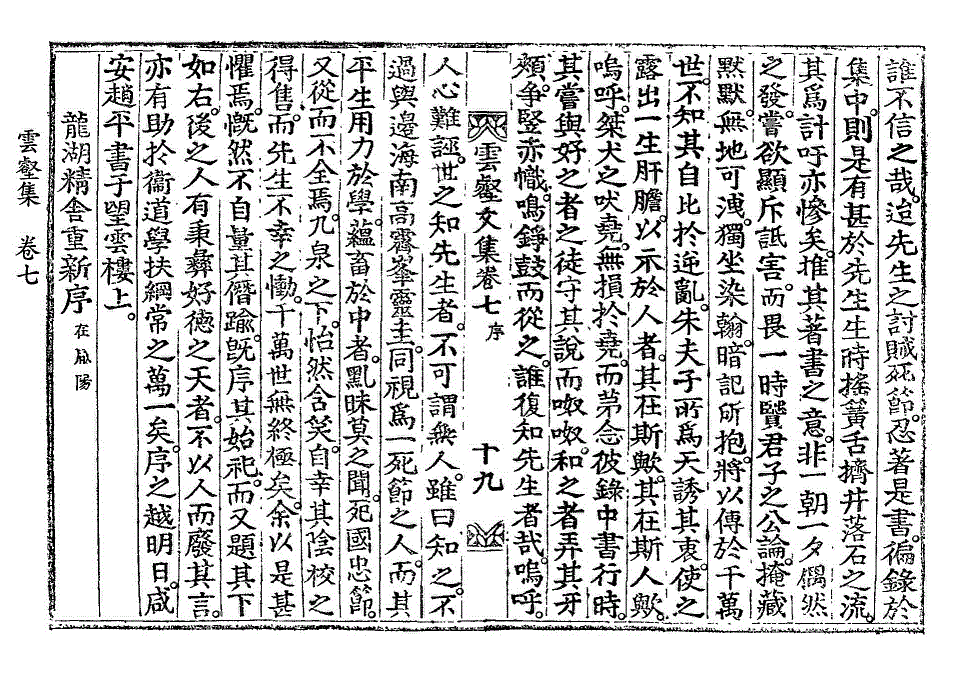 谁不信之哉。迨先生之讨贼死节。忍著是书。遍录于集中。则是有甚于先生生时摇簧舌挤井落石之流。其为计吁亦惨矣。推其著书之意。非一朝一夕偶然之发。尝欲显斥诋害。而畏一时贤君子之公论。掩藏默默。无地可泄。独坐染翰。暗记所抱。将以传于千万世。不知其自比于逆乱。朱夫子所为天诱其衷。使之露出一生肝胆。以示于人者。其在斯欤。其在斯人欤。呜呼。桀犬之吠尧。无损于尧。而第念彼录中书行时。其尝与好之者之徒守其说而呶呶。和之者弄其牙颊。争竖赤帜。鸣铮鼓而从之。谁复知先生者哉。呜呼。人心难诬。世之知先生者。不可谓无人。虽曰知之。不过与边海南高霁峰灵圭。同视为一死节之人。而其平生用力于学。蕴畜于中者。䵝昧莫之闻。死国忠节。又从而不全焉。九泉之下。怡然含笑。自幸其阴校之得售。而先生不幸之恸。千万世无终极矣。余以是甚惧焉。慨然不自量其僭踰。既序其始祀。而又题其下如右。后之人有秉彝好德之天者。不以人而废其言。亦有助于卫道学扶纲常之万一矣。序之越明日。咸安赵平书于望云楼上。
谁不信之哉。迨先生之讨贼死节。忍著是书。遍录于集中。则是有甚于先生生时摇簧舌挤井落石之流。其为计吁亦惨矣。推其著书之意。非一朝一夕偶然之发。尝欲显斥诋害。而畏一时贤君子之公论。掩藏默默。无地可泄。独坐染翰。暗记所抱。将以传于千万世。不知其自比于逆乱。朱夫子所为天诱其衷。使之露出一生肝胆。以示于人者。其在斯欤。其在斯人欤。呜呼。桀犬之吠尧。无损于尧。而第念彼录中书行时。其尝与好之者之徒守其说而呶呶。和之者弄其牙颊。争竖赤帜。鸣铮鼓而从之。谁复知先生者哉。呜呼。人心难诬。世之知先生者。不可谓无人。虽曰知之。不过与边海南高霁峰灵圭。同视为一死节之人。而其平生用力于学。蕴畜于中者。䵝昧莫之闻。死国忠节。又从而不全焉。九泉之下。怡然含笑。自幸其阴校之得售。而先生不幸之恸。千万世无终极矣。余以是甚惧焉。慨然不自量其僭踰。既序其始祀。而又题其下如右。后之人有秉彝好德之天者。不以人而废其言。亦有助于卫道学扶纲常之万一矣。序之越明日。咸安赵平书于望云楼上。龙湖精舍重新序(在咸阳)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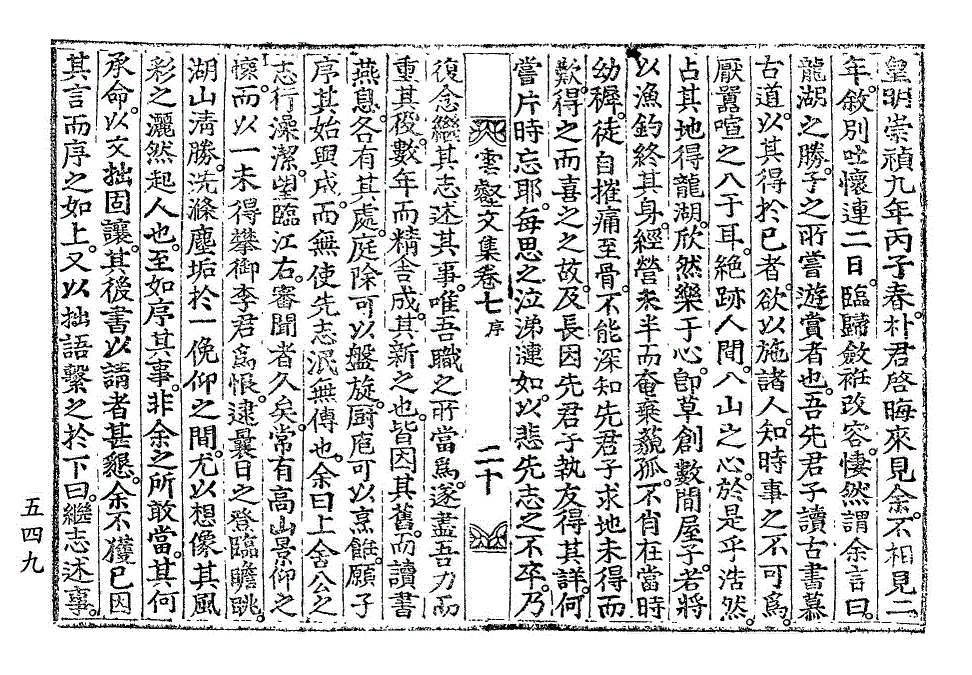 皇明崇祯九年丙子春。朴君启晦来见余。不相见二年。叙别吐怀连二日。临归敛衽改容。悽然谓余言曰。龙湖之胜。子之所尝游赏者也。吾先君子读古书慕古道。以其得于己者。欲以施诸人。知时事之不可为。厌嚣喧之入于耳。绝迹人间。入山之心。于是乎浩然。占其地得龙湖。欣然乐于心。即草创数间屋子。若将以渔钓终其身。经营未半而奄弃藐孤。不肖在当时幼稚。徒自摧痛至骨。不能深知先君子求地未得而叹。得之而喜之之故。及长因先君子执友得其详。何尝片时忘耶。每思之泣涕涟如。以悲先志之不卒。乃复念继其志述其事。唯吾职之所当为。遂尽吾力而重其役。数年而精舍成。其新之也。皆因其旧。而读书燕息。各有其处。庭除可以盘旋。厨庖可以烹饪。愿子序其始与成。而无使先志泯无传也。余曰上舍公之志行澡洁。望临江右。审闻者久矣。常有高山景仰之怀。而以一未得攀御李君为恨。逮曩日之登临瞻眺。湖山清胜。洗涤尘垢于一俛仰之间。尤以想像其风彩之洒然起人也。至如序其事。非余之所敢当。其何承命。以文拙固让。其后书以请者甚恳。余不获已因其言而序之如上。又以拙语系之于下曰。继志述事。
皇明崇祯九年丙子春。朴君启晦来见余。不相见二年。叙别吐怀连二日。临归敛衽改容。悽然谓余言曰。龙湖之胜。子之所尝游赏者也。吾先君子读古书慕古道。以其得于己者。欲以施诸人。知时事之不可为。厌嚣喧之入于耳。绝迹人间。入山之心。于是乎浩然。占其地得龙湖。欣然乐于心。即草创数间屋子。若将以渔钓终其身。经营未半而奄弃藐孤。不肖在当时幼稚。徒自摧痛至骨。不能深知先君子求地未得而叹。得之而喜之之故。及长因先君子执友得其详。何尝片时忘耶。每思之泣涕涟如。以悲先志之不卒。乃复念继其志述其事。唯吾职之所当为。遂尽吾力而重其役。数年而精舍成。其新之也。皆因其旧。而读书燕息。各有其处。庭除可以盘旋。厨庖可以烹饪。愿子序其始与成。而无使先志泯无传也。余曰上舍公之志行澡洁。望临江右。审闻者久矣。常有高山景仰之怀。而以一未得攀御李君为恨。逮曩日之登临瞻眺。湖山清胜。洗涤尘垢于一俛仰之间。尤以想像其风彩之洒然起人也。至如序其事。非余之所敢当。其何承命。以文拙固让。其后书以请者甚恳。余不获已因其言而序之如上。又以拙语系之于下曰。继志述事。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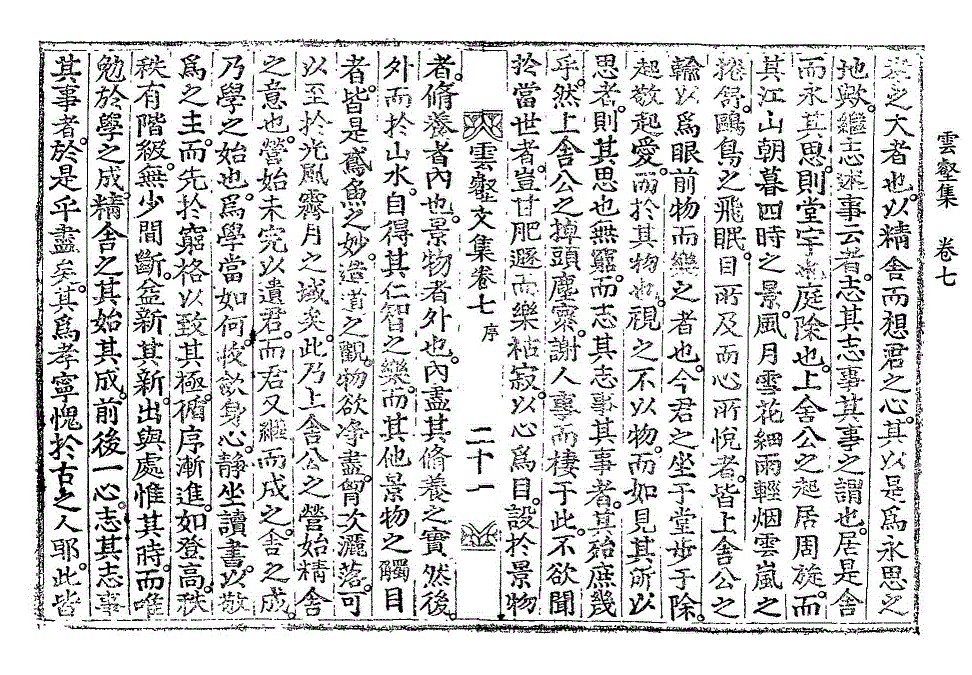 孝之大者也。以精舍而想君之心。其以是为永思之地欤。继志述事云者。志其志事其事之谓也。居是舍而永其思。则堂宇也庭除也。上舍公之起居周旋。而其江山朝暮四时之景。风月雪花细雨轻烟云岚之捲舒。鸥鸟之飞眠。目所及而心所悦者。皆上舍公之输以为眼前物而乐之者也。今君之坐于堂步于除。起敬起爱。而于其物也。视之不以物。而如见其所以思者。则其思也无穷。而志其志事其事者。其殆庶几乎。然上舍公之掉头尘寰。谢人事而栖于此。不欲闻于当世者。岂甘肥遁而乐枯寂。以心为目。设于景物者。脩养者内也。景物者外也。内尽其脩养之实然后。外而于山水。自得其仁智之乐。而其他景物之触目者。皆是鸢鱼之妙。造道之观。物欲净尽。胸次洒落。可以至于光风霁月之域矣。此乃上舍公之营始精舍之意也。营始未完以遗君。而君又继而成之。舍之成。乃学之始也。为学当如何。收敛身心。静坐读书。以敬为之主。而先于穷格以致其极。循序渐进。如登高。秩秩有阶级。无少间断。益新其新。出与处惟其时。而唯勉于学之成。精舍之其始其成。前后一心。志其志事其事者。于是乎尽矣。其为孝宁愧于古之人耶。此皆
孝之大者也。以精舍而想君之心。其以是为永思之地欤。继志述事云者。志其志事其事之谓也。居是舍而永其思。则堂宇也庭除也。上舍公之起居周旋。而其江山朝暮四时之景。风月雪花细雨轻烟云岚之捲舒。鸥鸟之飞眠。目所及而心所悦者。皆上舍公之输以为眼前物而乐之者也。今君之坐于堂步于除。起敬起爱。而于其物也。视之不以物。而如见其所以思者。则其思也无穷。而志其志事其事者。其殆庶几乎。然上舍公之掉头尘寰。谢人事而栖于此。不欲闻于当世者。岂甘肥遁而乐枯寂。以心为目。设于景物者。脩养者内也。景物者外也。内尽其脩养之实然后。外而于山水。自得其仁智之乐。而其他景物之触目者。皆是鸢鱼之妙。造道之观。物欲净尽。胸次洒落。可以至于光风霁月之域矣。此乃上舍公之营始精舍之意也。营始未完以遗君。而君又继而成之。舍之成。乃学之始也。为学当如何。收敛身心。静坐读书。以敬为之主。而先于穷格以致其极。循序渐进。如登高。秩秩有阶级。无少间断。益新其新。出与处惟其时。而唯勉于学之成。精舍之其始其成。前后一心。志其志事其事者。于是乎尽矣。其为孝宁愧于古之人耶。此皆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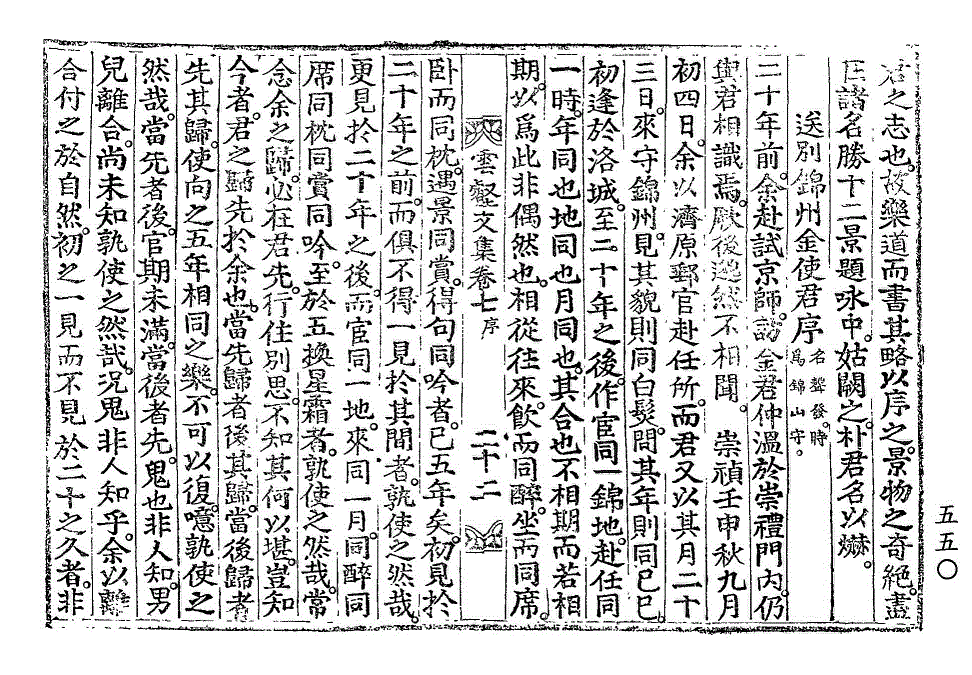 君之志也。故乐道而书其略以序之。景物之奇绝。尽在诸名胜十二景题咏中。姑阙之。朴君名以赫。
君之志也。故乐道而书其略以序之。景物之奇绝。尽在诸名胜十二景题咏中。姑阙之。朴君名以赫。送别锦州金使君序(名声发。时为锦山守。)
二十年前。余赴试京师。访金君仲温于崇礼门内。仍与君相识焉。厥后邈然不相闻。 崇祯壬申秋九月初四日。余以济原邮官赴任所。而君又以其月二十三日。来守锦州。见其貌则同白发。问其年则同己巳。初逢于洛城。至二十年之后。作宦同一锦地。赴任同一时。年同也地同也月同也。其合也不相期而若相期。以为此非偶然也。相从往来。饮而同醉。坐而同席。卧而同枕。遇景同赏。得句同吟者。已五年矣。初见于二十年之前。而俱不得一见于其间者。孰使之然哉。更见于二十年之后。而宦同一地。来同一月。同醉同席同枕同赏同吟。至于五换星霜者。孰使之然哉。常念余之归。必在君先。行住别思。不知其何以堪。岂知今者。君之归先于余也。当先归者后其归。当后归者先其归。使向之五年相同之乐。不可以复。噫孰使之然哉。当先者后。官期未满。当后者先。鬼也非人知。男儿离合。尚未知孰使之然哉。况鬼非人知乎。余以离合付之于自然。初之一见而不见于二十之久者。非
云壑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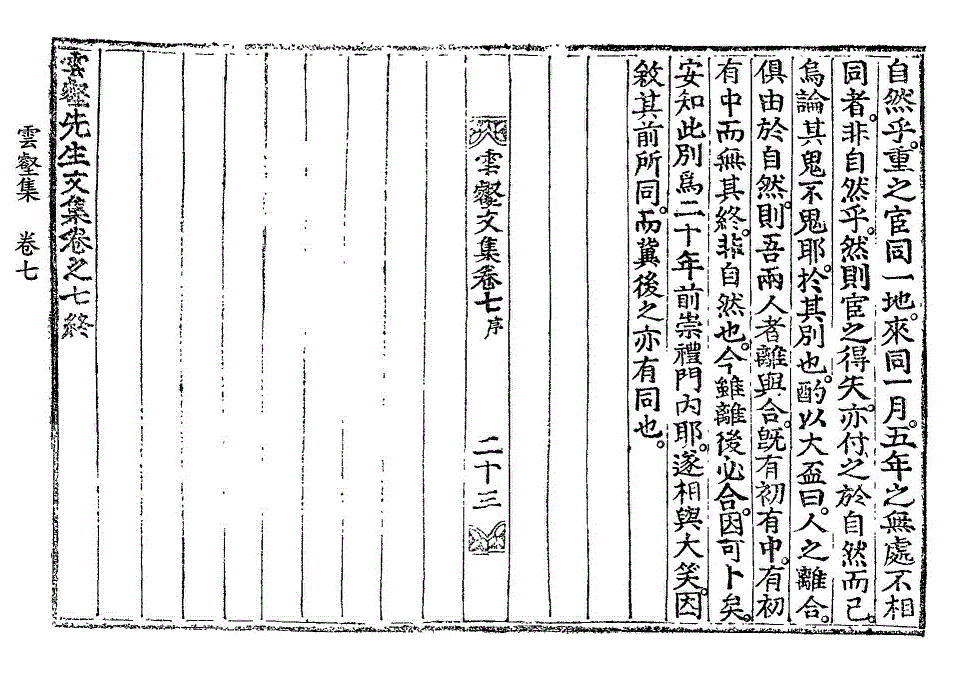 自然乎。重之宦同一地。来同一月。五年之无处不相同者。非自然乎。然则宦之得失。亦付之于自然而已。乌论其鬼不鬼耶。于其别也。酌以大杯曰。人之离合。俱由于自然。则吾两人者离与合。既有初有中。有初有中而无其终。非自然也。今虽离后必合。因可卜矣。安知此别为二十年前崇礼门内耶。遂相与大笑。因叙其前所同。而冀后之亦有同也。
自然乎。重之宦同一地。来同一月。五年之无处不相同者。非自然乎。然则宦之得失。亦付之于自然而已。乌论其鬼不鬼耶。于其别也。酌以大杯曰。人之离合。俱由于自然。则吾两人者离与合。既有初有中。有初有中而无其终。非自然也。今虽离后必合。因可卜矣。安知此别为二十年前崇礼门内耶。遂相与大笑。因叙其前所同。而冀后之亦有同也。